一、李瀷的学术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317 |
| 颗粒名称: | 一、李瀷的学术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8 |
| 页码: | 132-14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李瀷是朝鲜朝末期的朱子学者和西学研究者。他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但同时也进行了异端的西学研究。李瀷出身于南人名门世家,在政治党争中生活,家族受到冲击。他受到南人大黜陟事件的影响,放弃了科举考试,专心于读书和著述。他的学问主要基于朱子学,但也吸收了西学的知识,同时提出了一些社会改革的主张。李瀷的学问以性理学为核心,同时对西学表达了积极的评价。他提出了脑主知觉说和三魂论作为西学的核心命题,并对西洋的天文学和数学表示赞赏。李瀷还发展了心情论和四端七情论,吸收了李滉和李珥的思想,并将其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相结合。他将人心归属于知觉之心,将道心归属于理义之心,同时分析了心之构造。总的来说,李瀷在维持朱子学的同时,对于异端言论持包容态度,也认可了西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 |
| 关键词: | 李瀷 学术 朱子 |
内容
李瀷,字子新,自号星湖,祖籍为京畿道骊州,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朱子学者、西学者之一。[3]
(一)强烈的道统意识与异端的西学研究并存
李瀷的一生,经受了17世纪末激烈党争的冲击,他是经常生活在政治剧变之阴影中的两班知识人。其家族为科举合格者辈出的南人名门,曾祖父李尚毅为议政府左赞成,祖父李志安任司宪府持平。其父李夏镇亦为司宪府大司宪,肃宗六年(1680)遭遇了南人大黜陟(又称庚申大黜陟)事件,随之失职而被流放到平安道云山。
肃宗七年(1681),李瀷出生于其父的流放地。第二年,其父李夏镇去世,李瀷随母亲移居先祖坟墓所在的京畿道广州的瞻星里。李瀷资质聪颖,优于常人,但是生而病弱,无法外出就学,其学问主要得益于稍稍年长的仲兄李潜。
但是仲兄李潜于肃宗三十二年(1706),以老论金春泽等人企图危害王世子为由而上诉,要求撤换老论的右议政李颐明,引发了肃宗的愤怒,拷问之后而被杖杀。仲兄因党争而惨死,李瀷为此而受到极大的冲击,失去了立身出世以及关心世事的意愿,从而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学习,此后作为在野的学者而专心于读书和著述。英祖三年(1727),虽被推举为缮工监假监役,他力辞而无意仕进。英祖三十九年(1763)去世,享年83岁。
李瀷的学问大致由三方面组成:(1)在吸收朝鲜朱子学(性理学)一派的李滉(1501~1570)思想的同时,(2)对于欧洲传来的新知识(西学)亦有正面的评价,并以此展开了新考察,另外,(3)受到柳馨远等人经世论的影响,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主张。[4]
李瀷学问的根本在于性理学,[5]其学统属于退溪李滉→寒冈郑逑(1543~1620)→眉叟许穆(1595~1682)传承的畿湖南人一系。但是,李瀷不止于将自身的师承系于李退溪,而是从个人内心出发,十分仰慕退溪的学德。因此,李瀷模仿《近思录》编集了收录退溪言行的《李子粹语》,以及为退溪的四端七情论辩护的《四七新编》,从退溪的遗集中分类抄出与礼相关的书札而编纂了《李先生礼说类编》等。另外,李瀷希望通过研究经书和性理学书来把握真理,以供社会之实用。这一点可由保存下来的有关《诗经》《尚书》《周易》三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以及《家礼》《近思录》《心经》《小学》等大量读书笔记得以证明。《诗经疾书》《书经疾书》等便是此类著述。
李瀷将继承与发展朱子学说作为其一生的志向,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如果反朱子学者的异端言论中有不得不看之处,亦应当学习。他积极地学习西学,果断地利用西学知识来解释儒家经文,并提出多种社会改革论。真正的学者必须为了振兴正学而批判异端,但是李瀷不受此拘束,而是在了解异端的同时,视西学研究为学者之当为而予以肯定,不得不说这是作为朱子学者不应有的态度。
在维持朱子学所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之同时,对于必须拒斥的异端却予以宽容,关于这一点或许应当做这样的解释最为稳妥:“这是一种承认其他思想也有部分价值的有限的多价值主义。”[6]
(二)星湖西学的概要
朝鲜朝景宗四年(1724)春,慎后聃拜访李瀷而了解到所谓“西洋之学”,于是,多次就西学问题,与星湖发生了论争,相关记录便是《遯窩西学辨》。该书大致由《纪闻编》《灵言蠡勺辨》《天主实义辨》和《职方外纪辨》所组成。《纪闻编》的撰写目的在于介绍星湖西学的概要。
基于慎后聃的《纪闻编》,可以看出李瀷西学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虽然李瀷自身最终否定基督教神学,但并不认为西教是耶稣会的阴谋(“张伪教而陷一世”),西学以外的西教也可成为分析考察的对象。例如,尽管慎后聃批评“天堂地狱之说”等西教理论的荒唐性,但是李瀷却介绍了西学的“实用处”(科学内容)强调其有用性,拥护“利西泰之学”。这与后文讨论的洪大容认为西教不值一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特征是,将脑主知觉说(“头有脑囊,为记含之主”)与三魂论(“草木有生魂,禽兽有觉魂,人有灵魂”)作为西学的核心命题。[7]甲辰(1724)春,针对慎后聃的西学“以何为宗”的问题,李瀷自己以“论学之大要”提出上述二说,可见上述说法是可以确定的。另外,戊申(1728)春,慎后聃曾对李翊卫提及,李瀷认同这样的命题。
所谓脑主知觉说,即“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李瀷《星湖僿学类选》的《西国医》以汤若望《主制群征》(1629年刊行)为依据,论述了“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这一观点,将西医的脑主知觉说与东医的心主知觉说予以折中,认为在人类的两大精神作用中,“感觉与知觉的作用在脑,思考与理性的作用在心”(“觉在脑而知在心”)。另外他主张一身流行的形气粗大,主思的心气(心脏之气)则极其细微,而它们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所谓“三魂论”,这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灵魂论,认为草木只有生魂(生长之心,anima vegetabilis),禽兽有生魂(生长之心)和觉魂(知觉之心,anima senseitiva),人有生魂(生长之心)、觉魂(知觉之心)和灵魂(理义之心,anima rationalis)。若将《星湖全集》卷四十一的《心说》、卷五十四的《跋荀子》以及《星湖僿说类选》的《荀子》合而观之,毫无疑问,李瀷所说的三魂论的论据与《灵言蠡酌》《天主实义》的灵魂论以及《荀子·王制篇》的“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有义”非常相似。
第三个特征是,李瀷认为“天文筹数法”“星历象数学”是“发前人所未发”或“有前古之所未发者”,极其称赞。[8]乙巳(1725)秋,李瀷解说了十二重天、温带凉带、地圆、日月行度、去极远近等,并记述了日月食预报的正确性。另外他还指出,郑玄的“地厚三万里”与西历的“地围九万里”是暗合的。
李瀷对于西欧数理科学的称赞在《纪闻篇》以外的很多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比如根据安鼎福《天学问答》的附录,李瀷指出西欧的“天文推步、制造器皿、算数等术,非中夏之所及也”。尤其称赞“今时宪历法,可谓百代无弊”,“西国历法,非尧时历之可比也”。[9]
(三)星湖的四端七情论
李瀷的心情论、四端七情论是退溪以来朝鲜朱子学内在发展的优秀成果[10],但同时必须承认其性理学的命题中也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李瀷的四端七情论,虽说是沿袭李滉以来的理气范式,但是吸收了奇大升(1527~1572)开始倡导而由李珥(1536~1584)集大成的心发的理气不离的基本原理,并借此重新解释李滉主理的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具体到心情论所讨论的心之机能与构造的问题,李滉以宋代张载“心统性情”为理论根基,从“性”“\情”观点出发论心,而李珥受元代胡炳文“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大学章句大全·经一章》小注)的启发,与性、情一样重“意”。对此,李瀷则在性、情、意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论点的变化以及论题的扩大。这与朝鲜朱子学的不断扩大进而发生变质的发展趋向是吻合的。
1.三魂论的影响
李瀷为了证明李滉理气互发的合理性[11],提出了严格区分知觉与思考的公私二情论,即将人心(七情)归属于“知觉之心”(私情),而将道心(四端)归属于“理义之心”(公情)。另外,为了论证源自公私的人心道心说的合理性,通过草木之心、禽兽之心与人类之心的对比,分析人所具备的心之构造。[12]
在《心说》一文中,李瀷认为虽然土石是无心的,然而“人者,较之于草木而均有生长之心。较之于禽兽而有知觉之心。其义理之心,则彼草木禽兽所未有也”。又说:“至于人,其有生长及知觉之心,固与禽兽同,而又有所谓理义之心者。”在星湖看来,植物、动物与人类之心具有如下的分层构造:
草木仅有生长之心
禽兽有生长之心与知觉之心
人有生长之心、知觉之心与理义(义理)之心在李瀷看来,知觉之心为人心,即人情,而理义之心为道心,即四端。
李瀷所说的草木、禽兽、人类的进化分层的心论,其构造非常独特。显而易见,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在内容或构造上都基本相同。另外如前所述,李瀷曾经通过《灵言蠡酌》与《天主实义》学习了欧洲哲学的心情论(三魂论)。由此可以断定,李瀷的公私心学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2.脑囊论(大气小气说)的影响
李瀷在其四端七情论中,论述了心情的发现路径与感应路径,其发现路径由道心(四端)的理发(理直发)与人心(七情)的气发(形气发)的互发二路所构成;相对于此,感应路径则是伴随发现路径而来,两者都属于理气共发的“理发气随”一路。
李瀷提到,首先,性“感物而动”,此时生发作为“性之欲”的情(《礼记·乐记》),四端、七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吾性感于外物而动,而不与吾形气相干者,属之理发。外物触吾形气而后吾性始感而动者,属之气发。”(《四七新编·第八》)“四端不因形气而直发,故属之理发。七情理因形气发,则属之气发。”(《四七新编·重跋》)在李瀷看来,理发意味着理的直接发动,与此相对,情的发动即气发是外物触及形气即身体,从而产生身体感觉(由外部刺激产生的身体感觉),再传达至心,最后理(或者思考、理性)发动(可参见出于李瀷之手的《四端七情图》,如右图)。李瀷所说的气发,由触及形气(身体)而生发,故以此命名,但是从发生的主体来看,则依然是理发而已。
在李瀷看来,心的发现路径有理发(理直发)与气发(形气发)两路,但是紧随发现路径而来的感应路径则只有理发气随(理应气随)一路。他说:“理发气随,四七同然。而若七情,则理发上面更有一层苗脉。所谓形气之私是也。”(《四七新编·重跋》)“心之感应,只有理发气随一路而已。四七何尝有异哉!”(《答李汝谦庚申》)关于星湖心学的“心发”构造,可以表示如下:
四端=道心(道德的情感)理发气随
七情=人心(由知觉而生的情感)生于形气之私→理发气随
须注意的是,在李瀷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的心发说当中,就发现而言,讲的是理气互发;就感应而言,讲的则是理气共发。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理论上的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李瀷指出,七情气发之气是指形气,与理发气随之气并不相同;所谓七情之气发,是指理发气随的知觉依形气而发。他说“气有大小。形气之气属之身,气随之气属之心。形大而心小也。”(《答慎耳老辛酉》)这是说,形气(一身混沦之气)与心气(神明之气)在大小差异及灵妙上的不同,而其作用也是根本不同的。
尽管李瀷的二情论可以说是以二情的绝对区别为其特征的,但是之所以说二情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最终的感应路径(思考)虽然一样,但是其发现路径(知觉与思考)却是不同的,故而知觉与思考的作用部位是有差异的。李瀷自身虽未明言,但是不得不说一种心理学的命题,即如下的心理二重构造乃是其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细微的神明之气相关的构造是“心↔思考↔理发气随”,与缺乏灵妙的粗糙形气相关的是“脑↔感觉↔气发”。
如前所述,李瀷通过分析《主制群征》所说的西洋医学知识,了解到气有
图1《四端七情图》大小粗细,而大小的不同导致各自机能的差异;断定感觉与思考是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上述两个命题,都与星湖的人心道心论非常吻合。星湖在构建其公私心学之际,很有可能是援用了这两个命题,以此作为其思想的前提。这是因为心发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之模型,即“知觉之心”的一身流行的形气为大,“理义之心”心气为小,同时感觉与思考是来自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这完全可以对应于西欧的医学理论。
3.中西会通与西学的理论优越
李瀷作为朱子学学者,他坚信儒学在整体上的正确性(“无谬性”),同时作为西学者,他所追求的是更高层次上统一中西两学,即17~18世纪西学研究者共同的理想“中西会通”。因此在他的论述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从东亚视角出发,来实现东西理论的无矛盾统一,并以经学理论为优的立场来加以整合或折中。在上述的四端七情论以其及论文《天行健》和《跋职方外纪》当中,我们便能看到这样的主题。
(1)《天行健》
《星湖僿说·天地门》中的论文《天行健》根据《易经·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说明西欧传来的天动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此天动认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三垣二十八宿天、宗动天等,都是围绕宇宙中心的不动的地球而公转的。
李瀷认为,《广雅》载“天之距地二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则说“五亿三千三百七十八里有奇”。两种说法,何者为是,尽管今天难以确定,但是两说都主张天是巨大的物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天既然是巨大的物体,因此不可能一日一循环(“一日一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周即对“天动”提出疑问,其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庄子·天运》)因为在理论上,即便是“地动”说,也能很好地说明天文现象。
但是,中国宋代朱子对于同样的问题,指出“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即天一日一转,地亦随之而转,而不及天运一度13],最后说“今坐于地,但知地之不动。”(《朱子语类》卷八十六)[14]朱子的观点(据星湖,这是对“地动”说的否定)亦须深入思考。
进而言之,圣人著述的《易经·乾卦·大象》中有“天行健”之说。据此,由于“圣人无所不知”,因而所谓“天行健”,即指天之自动而不容怀疑,李瀷指出:“可信且从之”。
要之,李瀷以经书的“天行健”一句来驳斥科学命题的“地动”说[15],竭力宣扬当时已成西学定论的“天动”说。
(2)《跋职方外纪》
《星湖全集》卷五十五的《跋职方外纪》,以《中庸》的子思语为根据,主张地圆说的合理性,也提出了同样的论述。《职方外纪》是意大利人耶稣会士艾儒略增译、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1557~1626)所汇编的五卷本世界地理书,完成于明天启三年(1623),收于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另外一人李之藻(1565~1630)编纂的《天学初函·理编》。
李瀷的《跋职方外纪》,开首便引用了《中庸》第26章的“地,振河海而不泄”。[16]李瀷指出,子思的说法(前半部分)意味着,并非海洋在陆地中漂浮,而是陆地纳大海于自身。即便在溟海或渤海之外,海洋必然有底,其底部皆为陆地所构成。这与西洋人详细论证的说法相契合,没有丝毫差异。
大地将海洋收于其中而海水不外泄,这是因为大地处于天圆的中心位置。由于天由东向西一日一周,所以处于天之运转中的物体,势必因其向心力的作用,而不得不向中心集中。即所谓“在天之内者,其势莫不辏以向中”。地既不下坠也不上升,上下四周皆以地为下、以天为上,其原因是一样的。[17]
由海洋是附着于陆地的观点,便不难推出“地圆”的命题。因为若向西航行至极,终究将再次进入东海(所谓“航海穷西,毕竟得出东海”)。而且,如果在航海的途中观察星象,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天顶亦各有差异。因为南界星可以在低纬度看见,而无法在高纬度看见。
《职方外纪》记录了西洋人真实的航海记录。例如其中记录了阁龙(哥伦布)寻找到东方大地(实际是美洲,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墨瓦兰(麦哲伦)由东洋(实际是美洲)到达中国大陆(实际是亚细亚的马鲁古),绕地球一周(卷四“墨瓦蜡尼加总说”)等。了解到麦哲伦环球一周的事实,则“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
李瀷根据子思的话,否定了“天地载水而浮”(张衡《浑天仪》)的传统浑天说/天圆地方说,由此展开论述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但是,李瀷的理论也有含糊之处。因为如果反过来看李瀷的说明,也许以下的说法反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即以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为依据,来揭示《中庸》第26章中的一句话里所隐含的意思,以此否定了传统的浑天说/天圆地方说。《中庸》第26章的这句话只是说“地振河海而不泄”,然而根据李瀷的观点,所谓“地振河海而不泄”就是指“地圆”,这一理论相比“天行健”即“天动”的说法,更是一种强辩而已。
(3)西学优越说
李瀷在进行东西科学理论比较研究之际,虽以实现两者的无矛盾统一、以经学理论为优的融合/折中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并没有将儒学/朱子学作为审视标准而让其发挥强烈作用。当他面对异端的西欧科学理论的绝对优越性之际,他承认传统科学存在缺陷,并向本国的知识人简要说明了西欧科学的内容及其先进性。例如阐释日月蚀发生原因的《日月蚀辨》以及说明东西岁差、南北岁差的《跋天问略》等便是此类著作。
李瀷特别赞赏传到东方的欧洲星历象数之学,主张西欧科学确实优于东亚的传统科学。例如除《日月蚀辨》《跋天问略》等以外,他在《星湖僿说·天地门》的《中西历三元》中指出:“西国之历,中国殆不及也。泰西为最,回回次之。”同样,在《历象》中,他也指出:“今行时宪历,即西洋人汤若望所造。于是乎,历道之极矣。日月交蚀,未有差谬。圣人复生,必从之矣。”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他的西学优越说。另外,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言西学的优越性,但是以其优越性为前提的论述其实也非常多。例如《北极高下说》《论周礼土圭》《地毬》等都是如此。
从西学优越说的立场来看,笼统、含糊地主张东西一致,其实这种主张无非是一方面承认西学的相对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儒学/朱子学当中也有类似之说。在李瀷的科学论当中,西学优越性是默认的逻辑前提,而以李瀷为代表的东亚西学研究者的中西会通论则应理解为这样的理念或思想潮流的结果,即18世纪以来显著的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宏观宇宙论乃至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结果。
(一)强烈的道统意识与异端的西学研究并存
李瀷的一生,经受了17世纪末激烈党争的冲击,他是经常生活在政治剧变之阴影中的两班知识人。其家族为科举合格者辈出的南人名门,曾祖父李尚毅为议政府左赞成,祖父李志安任司宪府持平。其父李夏镇亦为司宪府大司宪,肃宗六年(1680)遭遇了南人大黜陟(又称庚申大黜陟)事件,随之失职而被流放到平安道云山。
肃宗七年(1681),李瀷出生于其父的流放地。第二年,其父李夏镇去世,李瀷随母亲移居先祖坟墓所在的京畿道广州的瞻星里。李瀷资质聪颖,优于常人,但是生而病弱,无法外出就学,其学问主要得益于稍稍年长的仲兄李潜。
但是仲兄李潜于肃宗三十二年(1706),以老论金春泽等人企图危害王世子为由而上诉,要求撤换老论的右议政李颐明,引发了肃宗的愤怒,拷问之后而被杖杀。仲兄因党争而惨死,李瀷为此而受到极大的冲击,失去了立身出世以及关心世事的意愿,从而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学习,此后作为在野的学者而专心于读书和著述。英祖三年(1727),虽被推举为缮工监假监役,他力辞而无意仕进。英祖三十九年(1763)去世,享年83岁。
李瀷的学问大致由三方面组成:(1)在吸收朝鲜朱子学(性理学)一派的李滉(1501~1570)思想的同时,(2)对于欧洲传来的新知识(西学)亦有正面的评价,并以此展开了新考察,另外,(3)受到柳馨远等人经世论的影响,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主张。[4]
李瀷学问的根本在于性理学,[5]其学统属于退溪李滉→寒冈郑逑(1543~1620)→眉叟许穆(1595~1682)传承的畿湖南人一系。但是,李瀷不止于将自身的师承系于李退溪,而是从个人内心出发,十分仰慕退溪的学德。因此,李瀷模仿《近思录》编集了收录退溪言行的《李子粹语》,以及为退溪的四端七情论辩护的《四七新编》,从退溪的遗集中分类抄出与礼相关的书札而编纂了《李先生礼说类编》等。另外,李瀷希望通过研究经书和性理学书来把握真理,以供社会之实用。这一点可由保存下来的有关《诗经》《尚书》《周易》三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以及《家礼》《近思录》《心经》《小学》等大量读书笔记得以证明。《诗经疾书》《书经疾书》等便是此类著述。
李瀷将继承与发展朱子学说作为其一生的志向,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如果反朱子学者的异端言论中有不得不看之处,亦应当学习。他积极地学习西学,果断地利用西学知识来解释儒家经文,并提出多种社会改革论。真正的学者必须为了振兴正学而批判异端,但是李瀷不受此拘束,而是在了解异端的同时,视西学研究为学者之当为而予以肯定,不得不说这是作为朱子学者不应有的态度。
在维持朱子学所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之同时,对于必须拒斥的异端却予以宽容,关于这一点或许应当做这样的解释最为稳妥:“这是一种承认其他思想也有部分价值的有限的多价值主义。”[6]
(二)星湖西学的概要
朝鲜朝景宗四年(1724)春,慎后聃拜访李瀷而了解到所谓“西洋之学”,于是,多次就西学问题,与星湖发生了论争,相关记录便是《遯窩西学辨》。该书大致由《纪闻编》《灵言蠡勺辨》《天主实义辨》和《职方外纪辨》所组成。《纪闻编》的撰写目的在于介绍星湖西学的概要。
基于慎后聃的《纪闻编》,可以看出李瀷西学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虽然李瀷自身最终否定基督教神学,但并不认为西教是耶稣会的阴谋(“张伪教而陷一世”),西学以外的西教也可成为分析考察的对象。例如,尽管慎后聃批评“天堂地狱之说”等西教理论的荒唐性,但是李瀷却介绍了西学的“实用处”(科学内容)强调其有用性,拥护“利西泰之学”。这与后文讨论的洪大容认为西教不值一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特征是,将脑主知觉说(“头有脑囊,为记含之主”)与三魂论(“草木有生魂,禽兽有觉魂,人有灵魂”)作为西学的核心命题。[7]甲辰(1724)春,针对慎后聃的西学“以何为宗”的问题,李瀷自己以“论学之大要”提出上述二说,可见上述说法是可以确定的。另外,戊申(1728)春,慎后聃曾对李翊卫提及,李瀷认同这样的命题。
所谓脑主知觉说,即“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李瀷《星湖僿学类选》的《西国医》以汤若望《主制群征》(1629年刊行)为依据,论述了“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这一观点,将西医的脑主知觉说与东医的心主知觉说予以折中,认为在人类的两大精神作用中,“感觉与知觉的作用在脑,思考与理性的作用在心”(“觉在脑而知在心”)。另外他主张一身流行的形气粗大,主思的心气(心脏之气)则极其细微,而它们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所谓“三魂论”,这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灵魂论,认为草木只有生魂(生长之心,anima vegetabilis),禽兽有生魂(生长之心)和觉魂(知觉之心,anima senseitiva),人有生魂(生长之心)、觉魂(知觉之心)和灵魂(理义之心,anima rationalis)。若将《星湖全集》卷四十一的《心说》、卷五十四的《跋荀子》以及《星湖僿说类选》的《荀子》合而观之,毫无疑问,李瀷所说的三魂论的论据与《灵言蠡酌》《天主实义》的灵魂论以及《荀子·王制篇》的“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有义”非常相似。
第三个特征是,李瀷认为“天文筹数法”“星历象数学”是“发前人所未发”或“有前古之所未发者”,极其称赞。[8]乙巳(1725)秋,李瀷解说了十二重天、温带凉带、地圆、日月行度、去极远近等,并记述了日月食预报的正确性。另外他还指出,郑玄的“地厚三万里”与西历的“地围九万里”是暗合的。
李瀷对于西欧数理科学的称赞在《纪闻篇》以外的很多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比如根据安鼎福《天学问答》的附录,李瀷指出西欧的“天文推步、制造器皿、算数等术,非中夏之所及也”。尤其称赞“今时宪历法,可谓百代无弊”,“西国历法,非尧时历之可比也”。[9]
(三)星湖的四端七情论
李瀷的心情论、四端七情论是退溪以来朝鲜朱子学内在发展的优秀成果[10],但同时必须承认其性理学的命题中也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李瀷的四端七情论,虽说是沿袭李滉以来的理气范式,但是吸收了奇大升(1527~1572)开始倡导而由李珥(1536~1584)集大成的心发的理气不离的基本原理,并借此重新解释李滉主理的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具体到心情论所讨论的心之机能与构造的问题,李滉以宋代张载“心统性情”为理论根基,从“性”“\情”观点出发论心,而李珥受元代胡炳文“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大学章句大全·经一章》小注)的启发,与性、情一样重“意”。对此,李瀷则在性、情、意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论点的变化以及论题的扩大。这与朝鲜朱子学的不断扩大进而发生变质的发展趋向是吻合的。
1.三魂论的影响
李瀷为了证明李滉理气互发的合理性[11],提出了严格区分知觉与思考的公私二情论,即将人心(七情)归属于“知觉之心”(私情),而将道心(四端)归属于“理义之心”(公情)。另外,为了论证源自公私的人心道心说的合理性,通过草木之心、禽兽之心与人类之心的对比,分析人所具备的心之构造。[12]
在《心说》一文中,李瀷认为虽然土石是无心的,然而“人者,较之于草木而均有生长之心。较之于禽兽而有知觉之心。其义理之心,则彼草木禽兽所未有也”。又说:“至于人,其有生长及知觉之心,固与禽兽同,而又有所谓理义之心者。”在星湖看来,植物、动物与人类之心具有如下的分层构造:
草木仅有生长之心
禽兽有生长之心与知觉之心
人有生长之心、知觉之心与理义(义理)之心在李瀷看来,知觉之心为人心,即人情,而理义之心为道心,即四端。
李瀷所说的草木、禽兽、人类的进化分层的心论,其构造非常独特。显而易见,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在内容或构造上都基本相同。另外如前所述,李瀷曾经通过《灵言蠡酌》与《天主实义》学习了欧洲哲学的心情论(三魂论)。由此可以断定,李瀷的公私心学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2.脑囊论(大气小气说)的影响
李瀷在其四端七情论中,论述了心情的发现路径与感应路径,其发现路径由道心(四端)的理发(理直发)与人心(七情)的气发(形气发)的互发二路所构成;相对于此,感应路径则是伴随发现路径而来,两者都属于理气共发的“理发气随”一路。
李瀷提到,首先,性“感物而动”,此时生发作为“性之欲”的情(《礼记·乐记》),四端、七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吾性感于外物而动,而不与吾形气相干者,属之理发。外物触吾形气而后吾性始感而动者,属之气发。”(《四七新编·第八》)“四端不因形气而直发,故属之理发。七情理因形气发,则属之气发。”(《四七新编·重跋》)在李瀷看来,理发意味着理的直接发动,与此相对,情的发动即气发是外物触及形气即身体,从而产生身体感觉(由外部刺激产生的身体感觉),再传达至心,最后理(或者思考、理性)发动(可参见出于李瀷之手的《四端七情图》,如右图)。李瀷所说的气发,由触及形气(身体)而生发,故以此命名,但是从发生的主体来看,则依然是理发而已。
在李瀷看来,心的发现路径有理发(理直发)与气发(形气发)两路,但是紧随发现路径而来的感应路径则只有理发气随(理应气随)一路。他说:“理发气随,四七同然。而若七情,则理发上面更有一层苗脉。所谓形气之私是也。”(《四七新编·重跋》)“心之感应,只有理发气随一路而已。四七何尝有异哉!”(《答李汝谦庚申》)关于星湖心学的“心发”构造,可以表示如下:
四端=道心(道德的情感)理发气随
七情=人心(由知觉而生的情感)生于形气之私→理发气随
须注意的是,在李瀷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的心发说当中,就发现而言,讲的是理气互发;就感应而言,讲的则是理气共发。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理论上的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李瀷指出,七情气发之气是指形气,与理发气随之气并不相同;所谓七情之气发,是指理发气随的知觉依形气而发。他说“气有大小。形气之气属之身,气随之气属之心。形大而心小也。”(《答慎耳老辛酉》)这是说,形气(一身混沦之气)与心气(神明之气)在大小差异及灵妙上的不同,而其作用也是根本不同的。
尽管李瀷的二情论可以说是以二情的绝对区别为其特征的,但是之所以说二情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最终的感应路径(思考)虽然一样,但是其发现路径(知觉与思考)却是不同的,故而知觉与思考的作用部位是有差异的。李瀷自身虽未明言,但是不得不说一种心理学的命题,即如下的心理二重构造乃是其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细微的神明之气相关的构造是“心↔思考↔理发气随”,与缺乏灵妙的粗糙形气相关的是“脑↔感觉↔气发”。
如前所述,李瀷通过分析《主制群征》所说的西洋医学知识,了解到气有
图1《四端七情图》大小粗细,而大小的不同导致各自机能的差异;断定感觉与思考是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上述两个命题,都与星湖的人心道心论非常吻合。星湖在构建其公私心学之际,很有可能是援用了这两个命题,以此作为其思想的前提。这是因为心发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之模型,即“知觉之心”的一身流行的形气为大,“理义之心”心气为小,同时感觉与思考是来自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这完全可以对应于西欧的医学理论。
3.中西会通与西学的理论优越
李瀷作为朱子学学者,他坚信儒学在整体上的正确性(“无谬性”),同时作为西学者,他所追求的是更高层次上统一中西两学,即17~18世纪西学研究者共同的理想“中西会通”。因此在他的论述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从东亚视角出发,来实现东西理论的无矛盾统一,并以经学理论为优的立场来加以整合或折中。在上述的四端七情论以其及论文《天行健》和《跋职方外纪》当中,我们便能看到这样的主题。
(1)《天行健》
《星湖僿说·天地门》中的论文《天行健》根据《易经·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说明西欧传来的天动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此天动认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三垣二十八宿天、宗动天等,都是围绕宇宙中心的不动的地球而公转的。
李瀷认为,《广雅》载“天之距地二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则说“五亿三千三百七十八里有奇”。两种说法,何者为是,尽管今天难以确定,但是两说都主张天是巨大的物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天既然是巨大的物体,因此不可能一日一循环(“一日一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周即对“天动”提出疑问,其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庄子·天运》)因为在理论上,即便是“地动”说,也能很好地说明天文现象。
但是,中国宋代朱子对于同样的问题,指出“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即天一日一转,地亦随之而转,而不及天运一度13],最后说“今坐于地,但知地之不动。”(《朱子语类》卷八十六)[14]朱子的观点(据星湖,这是对“地动”说的否定)亦须深入思考。
进而言之,圣人著述的《易经·乾卦·大象》中有“天行健”之说。据此,由于“圣人无所不知”,因而所谓“天行健”,即指天之自动而不容怀疑,李瀷指出:“可信且从之”。
要之,李瀷以经书的“天行健”一句来驳斥科学命题的“地动”说[15],竭力宣扬当时已成西学定论的“天动”说。
(2)《跋职方外纪》
《星湖全集》卷五十五的《跋职方外纪》,以《中庸》的子思语为根据,主张地圆说的合理性,也提出了同样的论述。《职方外纪》是意大利人耶稣会士艾儒略增译、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1557~1626)所汇编的五卷本世界地理书,完成于明天启三年(1623),收于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另外一人李之藻(1565~1630)编纂的《天学初函·理编》。
李瀷的《跋职方外纪》,开首便引用了《中庸》第26章的“地,振河海而不泄”。[16]李瀷指出,子思的说法(前半部分)意味着,并非海洋在陆地中漂浮,而是陆地纳大海于自身。即便在溟海或渤海之外,海洋必然有底,其底部皆为陆地所构成。这与西洋人详细论证的说法相契合,没有丝毫差异。
大地将海洋收于其中而海水不外泄,这是因为大地处于天圆的中心位置。由于天由东向西一日一周,所以处于天之运转中的物体,势必因其向心力的作用,而不得不向中心集中。即所谓“在天之内者,其势莫不辏以向中”。地既不下坠也不上升,上下四周皆以地为下、以天为上,其原因是一样的。[17]
由海洋是附着于陆地的观点,便不难推出“地圆”的命题。因为若向西航行至极,终究将再次进入东海(所谓“航海穷西,毕竟得出东海”)。而且,如果在航海的途中观察星象,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天顶亦各有差异。因为南界星可以在低纬度看见,而无法在高纬度看见。
《职方外纪》记录了西洋人真实的航海记录。例如其中记录了阁龙(哥伦布)寻找到东方大地(实际是美洲,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墨瓦兰(麦哲伦)由东洋(实际是美洲)到达中国大陆(实际是亚细亚的马鲁古),绕地球一周(卷四“墨瓦蜡尼加总说”)等。了解到麦哲伦环球一周的事实,则“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
李瀷根据子思的话,否定了“天地载水而浮”(张衡《浑天仪》)的传统浑天说/天圆地方说,由此展开论述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但是,李瀷的理论也有含糊之处。因为如果反过来看李瀷的说明,也许以下的说法反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即以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为依据,来揭示《中庸》第26章中的一句话里所隐含的意思,以此否定了传统的浑天说/天圆地方说。《中庸》第26章的这句话只是说“地振河海而不泄”,然而根据李瀷的观点,所谓“地振河海而不泄”就是指“地圆”,这一理论相比“天行健”即“天动”的说法,更是一种强辩而已。
(3)西学优越说
李瀷在进行东西科学理论比较研究之际,虽以实现两者的无矛盾统一、以经学理论为优的融合/折中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并没有将儒学/朱子学作为审视标准而让其发挥强烈作用。当他面对异端的西欧科学理论的绝对优越性之际,他承认传统科学存在缺陷,并向本国的知识人简要说明了西欧科学的内容及其先进性。例如阐释日月蚀发生原因的《日月蚀辨》以及说明东西岁差、南北岁差的《跋天问略》等便是此类著作。
李瀷特别赞赏传到东方的欧洲星历象数之学,主张西欧科学确实优于东亚的传统科学。例如除《日月蚀辨》《跋天问略》等以外,他在《星湖僿说·天地门》的《中西历三元》中指出:“西国之历,中国殆不及也。泰西为最,回回次之。”同样,在《历象》中,他也指出:“今行时宪历,即西洋人汤若望所造。于是乎,历道之极矣。日月交蚀,未有差谬。圣人复生,必从之矣。”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他的西学优越说。另外,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言西学的优越性,但是以其优越性为前提的论述其实也非常多。例如《北极高下说》《论周礼土圭》《地毬》等都是如此。
从西学优越说的立场来看,笼统、含糊地主张东西一致,其实这种主张无非是一方面承认西学的相对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儒学/朱子学当中也有类似之说。在李瀷的科学论当中,西学优越性是默认的逻辑前提,而以李瀷为代表的东亚西学研究者的中西会通论则应理解为这样的理念或思想潮流的结果,即18世纪以来显著的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宏观宇宙论乃至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结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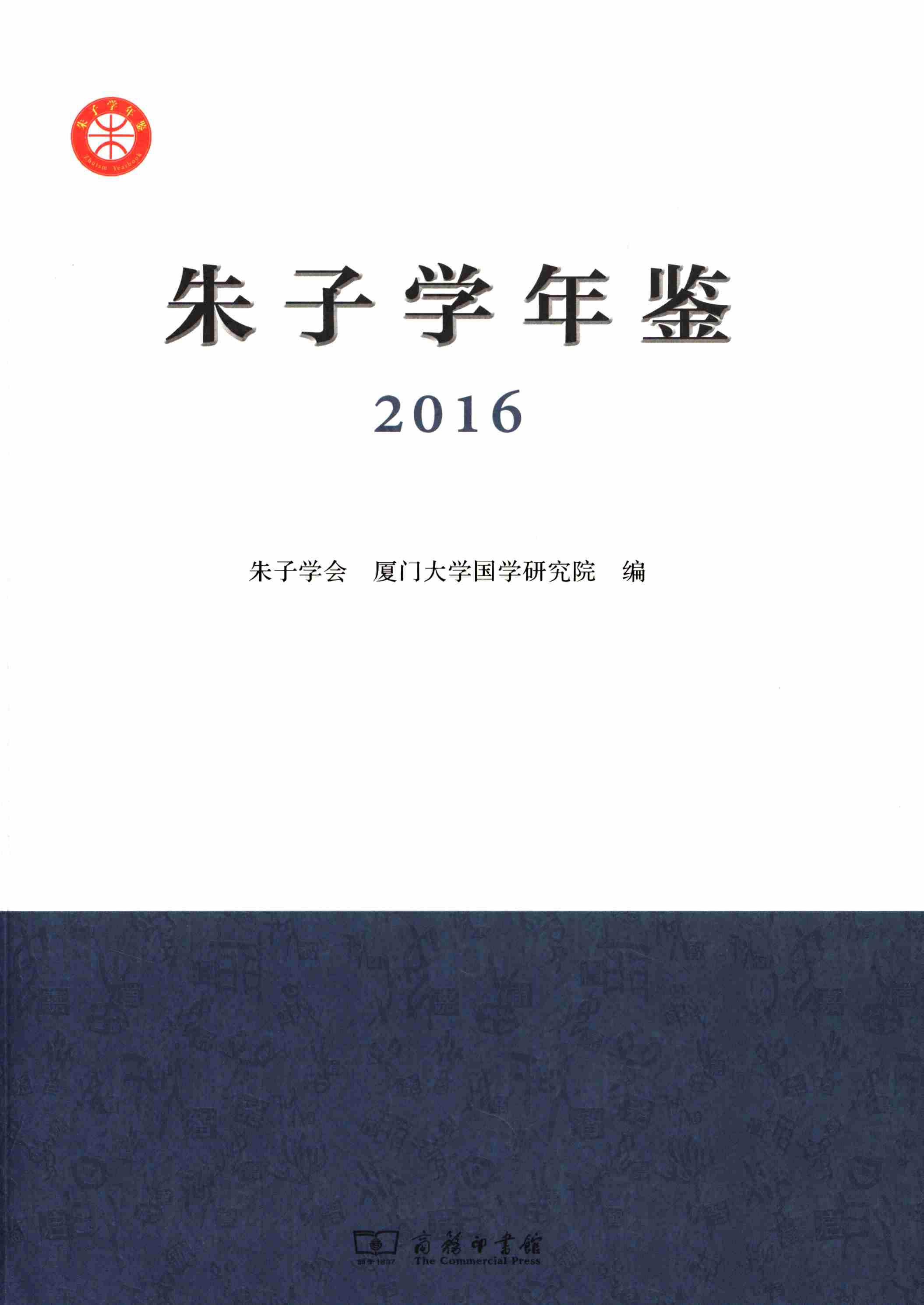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