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310 |
| 颗粒名称: | “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1 |
| 页码: | 111-131 |
| 摘要: | 本文主要讨论了朱熹的学术地位以及《四书大全》在明代经学中的重要性。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分析《四书大全》征引的人物系谱和相关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朱熹门人领袖黄榦在朱学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北山一系学人则是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了北山四先生之四书学的特点和贡献,强调了他们在朱学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作者还指出了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最后,作者总结了朱学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的历史背景和传承发展过程,并探讨了《四书大全》在明代经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
| 关键词: | 朱熹 四书 《四书大全》 |
内容
一、前言
北宋诸儒昂然奋起,证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学发展历程中精彩的一页。濂、洛、关、闽相继而起,成就斐然,然而汇聚成果,有赖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重构经典工作[1],自此由理学入于经学,由讲论而及于经典诠释,成为儒学后续发展的重要事业,朱学传布与四书讲论,乃是一体之工作。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刘爚奏请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国学[2],理宗淳祐元年(1241)诏入学宫从祀,云:“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3]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颁《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定本。[4]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场试四书义,四书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宋代沦亡,元代继起,元朝既没,明朝接续,朝代不同,但都推崇四书,四书成为宋元以降学术核心。后人往往以政治威势来解释朱熹地位的提升,认为朱熹学术乃出于官方表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庆元党禁、局势汹汹之际,无法想象日后学脉得以延伸,学术得以拓展的情形,钱穆先生“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专以科举功令为说”[6],乃是相当深入中肯的说法。朱熹的坚持与门人后学的传播,印证义理,蓄积力量,由民间而及于官方,才是建立四书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7]南宋推崇朱熹学术,来自于既压复起,还以公道,恢复朱熹名誉;元代表彰《四书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取用乃是怀柔兼纳的手段而已,用意在于笼络士子。[8]同尊朱学,程度与用意不同,真正确立朱熹学术地位,主要来自于明朝态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旧,深有恢复传统的意义,考试以朱学为宗,已具气氛,然而贯彻帝王意志,以皇权威势整合歧异,建立朱熹为尊的经说体系,主要来自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等人纂修《四书大全》[9]。自此,朱熹成为学术宗主,四书成为后代最重要经典,《四书大全》成为明代士人成学、入仕最重要的经说依据。[10]《四书大全》的地位无可比拟,检视明儒言论,邹元标《愿学集》云:“惧学者溺于异指,令童习家学,见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图无疆之治。”[11]高攀龙《高子遗书》云:“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12]指出皇权政教一体之事实。清人陆陇其甚至直指:“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13]一学术,同风俗,明显可见政治操作的影响,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四书大全》,明代“官学化”的结果便是确立四书成为最重要经典。就经学发展而言,唐代《五经正义》整合义疏,完成经学统一,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之为“经学统一时代”[14];至于明代以《四书大全》统合元儒经说,皮氏以“积衰时代”[15]来称呼明朝经学,认为其为败坏学风的源头,立场明显矛盾。事实上,《四书大全》整合宋元四书讲论内容,一如《五经正义》统合汉魏以降的经疏成果。唐承汉魏,明继宋元,落实经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经典文本,具有同样的学术发展意义,然却深受误解!为求厘清,笔者针对《四书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核以《宋元学案》,撰成《〈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16],分析庞大征引来源,探究朱熹门人结集之后学脉、宗派而及于宗族乡里情怀不同阶段的传衍线索,得出结论:黄榦传学何基,北山一系称为朱学“嫡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具有由宋入元,巩固学脉正传的地位,也具有确立朱学内涵的意义。《四书大全》征引共计106家,其中名列《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其中征引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四书大全》建立诠释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得以溯及朱熹的关键,对于掌握义理方向深有启示。
二、北山四先生之四书学
朱熹之后,黄榦为学门领袖。[17]朱学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最为重要,他们代表了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统计朱熹门人籍贯分布,以第一传门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传门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传门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传门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传门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18]可见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朱学由福建往传浙江,影响日趋深远,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按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19]黄百家(1643~1709)按语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峯亦高弟也。双峯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20]
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成为宋元朱学传播的中心,从脉络渊源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华人,从父命师事黄榦,黄榦勉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于病革之际对弟子的期许[21]。何基撰有《中庸发挥》《大学发挥》《论语发挥》,惜皆亡佚。核其语录,云:
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敬五事则明明德也,厚八政则新民也,建皇极则止至善也;至学皇极,有休征而无咎征,有仁寿而无鄙殀,则中和位育之应,皇极之极功也。
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中《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22]
前者发挥四书义理,后者深化四书义涵,不论是扩之于外或是究之于内,皆是以四书作为学术核心,《四书章句集注》与《朱子语类》相参的路径,更是指引后世解读朱熹四书学非常重要的方向[23],无怪乎黄宗羲按语云: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犹不满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应聘讲,第恐无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则,若人者,皆不
熟读四书之故也。”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24]
何基守之既严,甚至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树立熟读四书的学门宗风,正是传自黄榦学术的证明。
何基学术传于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王柏关注四书态度不变,同样强调必须深究其内而不必旁伸于外,语录云:“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盖深求之于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25]即可为证。王柏崇信四书的立场并无改易,不过细节上显然已有不同的思考,“虽曰”一句已透露端倪。王柏重视四书经文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甚于朱熹,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中庸》当依《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庸说》二篇,以“诚明”以下别为一篇[26,相歧之处,皆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义理诠释的重点。然而王柏尝试从结构化解改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王柏有关四书类著作,有《订古中庸》《论语衍义》《论语通旨》《鲁经章句》《孟子通旨》《标注四书》等,可惜大都亡佚。重构四书文本,其实是延续朱熹思考的结果,只是背离朱熹说法,尊背注而求经,奉与违戾之间,立场不免令人疑惑。[27]
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柳贯《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云:
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语孟子考证》。[28]
补充名物,以备考证,用意在于补充而非阐释。《宋元学案》黄百家按语云:
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历时既久,思之甚深,诸多说法前后不同,甚至留有诸多待解之处,临终前为《大学》“诚意”章费心竭虑,更是人所熟知之事[30]。后人延续思考方向,尝试解决经典文本与注解诠释问题,乃是学术发展的常态。黄百家申明后人应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迹,无疑是通达而且正确的看法。金氏既守朱学之教,又发四书之义,有关四书之著作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其中《大学章句疏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皆收于《四库全书》之中。金履祥传之许谦,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矣”[31],皆是朱学核心要义,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许谦于四书亦颇有心得,黄溍云: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敷绎义理,惟务平实。每戒学者曰:“士之为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至于进修利钝,则视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舍其书,何以得其心乎?圣贤之心,尽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立言,辞约意广,读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贸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觉其意初不与己异,愈久而所得愈深,与己意合者亦大异于初矣。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约意广,深嚼有味,许谦推崇至极,由朱子而得四书义理,由四书而得见圣人,饶富义理进程,只是许谦发挥义理,并不墨守朱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33]重视四书,强调朱子,也留意缺失,补正朱注。[34]许谦有关四书著作有《中庸丛说》《大学丛说》《读四书丛说》。《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说》只是四卷残本,阮元从元板影录《论语丛说》三卷,又从吴中藏书家得元版《中庸丛说》足本二卷。[35]北山学脉由宋而及元,脉络清楚于此可见: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黄榦接续朱熹,设教讲学,推究义理,昂然挺立,成为宋元之际最重要的朱学重镇,一方面传播朱学,延伸学脉;另一方面阐释义理,开展议题,证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价值。诚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汉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于同也。[36]
以动态方式看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同之与异,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无古今,学无先后,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仆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37]。既不执拘定见,又深化朱学成果,四书遂有多元丰富之诠释内容。朱学由宋入元,由注进入疏解的阶段,学人在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辩证,不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深化,贡献良多,无怪乎明代章一阳以“正学渊源”为名,纂辑四先生著作《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38],视之为由宋及元四书学发展一个重要环节;清代戴锜亦以洙泗、濂洛、关闽、北山为一脉相承之体系,其云:
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洙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弗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歧途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干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39]
承袭濂、洛、关、闽,儒学得传,北山一脉学人地位于此可见。
三、《四书大全》征引之北山学脉
《四书大全》征引当中,名列《宋元学案》之《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征引情形如下:
征引量共计154条。北山一系学人的著作如今多数已经不传,《四书大全》征引其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朱子学发展当中,北山一脉具有衔接朱门与后学的作用,对此后人深有共识。吴师道为许谦《读四书丛说》撰序言之甚明,其云:
《读四书丛说》者,金华白云先生许君益之为其徒讲说,而其徒记之之编也。君师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师鲁斋王先生柏,从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门,北山则学于勉斋黄公,而得朱子之传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中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之后,不泯灭而就微,则泮涣而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41],对于后世建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方式,具有关键地位。明代《四书大全》援取疏解内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际朱学传布情形,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体系,未见何基言论,恐与何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42]的态度有关。至于王柏、金履祥、许谦当中,许谦征引最多,则是因为许谦为入元之后发扬朱学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学列传》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43]
许谦于元代,讲学四十载,授徒著录千余人,发扬朱学不遗余力,撰作既丰,成果斐然,成为《四书大全》重要征引对象,乃是理所当然。此外,北山一系学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欧阳玄、何梦桂(《四书通》《四书大全》皆作何梦贵)、方逢辰三人。欧阳玄,字原功,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博,列于“仁山门人”,有《圭斋文集》传世。方逢辰,字君锡,学者称蛟峰先生,学术“以格物为穷理之本,以笃行为修己之实,终身顾未尝有师承”[44,然而父亲方镕为“朱学续传”,家学渊源,同是朱学一脉:
彼亦有以颖悟为道,以卤莽灭裂为学者,其说谓:“不由阶级,不假修为。”以致知格物为支离,以躐等陵节为易简,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匪徒诬人,亦以自诬,天下未有一超径诣忽焉而圣贤者。
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学之博以积之,反之约以一之。[45]
重申格致之教,阐明穷理之功。由四书而六经,学而有序,归之于理,提供了一条有进程、有境界的儒学道路,体系俨然。至于易简之教,直接圣人,不仅是自诬,而且也诬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陆,立场至为明显。然而于学术推展,北山一脉学人彰显朱学,也有与陆学争是非的意义。何梦桂,字岩叟,学者称潜斋先生,与方逢辰为讲友,宋亡不仕,于艰困之中昂扬挺立,于家国沦亡之际慨然承传,在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具有以身体道的实践意义。[46]事实上,朱熹对于吕祖谦死后的浙东学风深有疑虑,永康功利之学、永嘉事功之学继之而起,一重实利,一重实事,然而求之于外的结果,违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为利所诱。为求厘清,朱熹特别表彰金华先儒范浚,并将《心箴》载于《孟子集注》当中,以乡贤前辈的名望对治后学驰功逐利的缺失,期许从功利之中回归于人心救赎。47可见往浙东开展乃是朱熹夙愿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学人由黄榦而继承朱学,另一方面浙东本身也有其学术传统,吕祖谦于丽泽书院和明招堂讲学,门人众多[48]。金华原就是众多学派思潮交会之地,陆学、永康学、永嘉学相互交流,深有调和色彩。《朱子语录》卷122载有朱熹之分析,其云: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而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吕祖谦兼纳博采,重史轻经,成为浙东学术的特色。然而朱熹认为根源不明,不免于关键处偏失,而重权谋,求功利的结果,则不免让人违弃仁义,最终让人误以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论语》救治偏蔽,强调在日用之际,在心念之间,高举仁义价值,坚持儒学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后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也是采取相同立场。朱熹对于浙东学风深有忧虑,于此可见。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为标题,说明朱熹于南宋尚虚、尚实学风之间,展开全方位文化论战,在南宋纷然并起的学术社群当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颇能说明朱熹学术的方向。[49]而门人黄榦往浙东传学,不仅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北山一系学人习之有验的结果,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熹学术最终得以胜出。只是学术面相更为复杂,朱学既从北山一系学人而深入于浙学,却也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诠释方式,学术既延伸又相互影响,也就无怪乎《宋元学案》黄百家一方面有“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有“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的观察,甚至于最后又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50]。黄百家出于浙学,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学于浙学发展中入于史,通于文[51],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四书义理愈加丰富,却也渐生歧见,其中矛盾,正来自于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的结果,尤其后人缺乏朱熹融铸义理、思之甚深的历程[52],各自揣想之下,于经文兴发议论,时见新意,也时有误解,甚至以纠弹朱熹说法作为个人学术成就,不仅混淆朱熹四书义理体系,也造成后人了解的困扰。此一情形,从后人论述当中可以得见。邓文原《四书通序》云:“近世为图为书者益众,大抵于先儒论著及朱子取舍之说有所未通,而遽为臆说,以衒于世。余尝以谓,昔之学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学者常患其不胜古人,求胜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53]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云:“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54]议论纷出,各立门户,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学人。“争奇取异”的结果,孰为正解,顿成经典诠释的重要问题。以朱熹为宗成为后人最终的方向,回归于朱学则成为建构诠释主轴最重要的诉求,此一主张于新安一系宗主乡贤前辈的气氛中开展[55],而于明代完成。明代四书官学化过程中,确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种整合学术的手段,也是尝试解决朱学传衍问题的途径。[56]发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书经说内容,于后人剔除歧出、化异求同的调整当中,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四书大全》申明朱熹四书体系,阐释朱熹诠释经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学术传衍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发展意义。
四、诠释转折与开展
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金履祥考证四书的内容,《四书大全》收录不多,有关名物训诂的资料,《四书大全》以张存中《四书通证》为主,原因所在,可以由其言“学者于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于《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着所出”[57]一窥端倪。考证后出转精,张存中以补其所出的角度,内容更为丰富,自然成为《四书大全》取用材料。至于王柏有关《大学》《中庸》文本结构的调整,也并未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材料当中,显然关注所在,已有不同。其次,以征引的数目分析,《四书大全》征引许谦材料,《大学》29条,《中庸》34条,《论语》22条,《孟子》33条,数目相当平均,然而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分量之悬殊,即可发觉其中有异。许谦有关《大学》《中庸》诠释成果,征引比例明显较高,如果与其他人加总计算,《大学》42条、《中庸》43条、《论语》30条、《孟子》39条,《大学》《中庸》征引比例明显偏多,至于《论语》则明显偏少。检核《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大学》《中庸》各有一卷,《论语》四卷、《孟子》四卷,共计十卷,《论语》《孟子》并无空缺,经过后人筛选拣择,《四书大全》似乎更加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诠释成果,而对于《论语》《孟子》部分关注不深。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四书进程、体系与境界的讨论,对于四书义理的兴趣,高于日用之间、事理之际的体悟。朱熹对于浙东学术曾有“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28]的针砭语,似乎也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当中。事实上,检视《四书大全》列举方式,小注以朱熹《语类》、《或问》内容为主,后文辅以弟子门人意见,最末则以“云峰胡氏”“新安陈氏”“东阳许氏”等元儒诠释作结。分析征引结构,前者可见朱熹讲论之义理方向,后者可见训诂与体例的补充,形成朱熹、门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经说体系,元儒经说部分,多数依循饶鲁、新安、北山三系为序,而许谦说法往往列于征引之末,借以阐明章旨的价值与意义。可见北山一系作为朱学由宋而及元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成为后人讨论的基础。后人赓续推究,进行更全面的四书义理思索,其中排序并非偶然。北山一系学人深化与开展之处,列举如下:
(一)推究工夫进程
训解经文为《四书大全》征引内容的大宗,收录北山一系学者意见也以此类说解最多。分析语意,也辩证义理,北山学人一脉相承,经典诠释有继承发展的现象。《大学章句》朱注“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引许谦、方逢辰云:
严密,是严厉缜密。武毅,是刚武强毅。以恂栗释瑟僩,而朱子谓恂栗者,严敬存乎中,金仁山谓所守者严密,所养者刚毅,严密是不麤疏,
武毅是不颓惰,以此展转体认,则瑟僩之义可见。
瑟是工夫细密,僩是工夫强毅,恂栗是兢兢业业。惟其兢业戒惧,所以工夫精密而强毅[59]。
金履祥分出所守所养有严密与刚毅的不同,许谦、方逢辰的诠释乃是承前发展。《孟子集注·告子上》“乡为身死而不受”章引许谦云:
三乡为身,北山先生作一读,言乡为辱身失义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为身外之物,施惠于人,而受失义之禄乎,可谓无良心矣。[60]
申明经旨,乃是引用何基说法,诠释层层累聚,于此可见。北山一系学人彰显经典旨趣,揭示其中要旨,最终往往归于修养工夫的思考。《大学章句》“《诗》云:‘瞻彼淇澳’”章引许谦云:
此节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谓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绪,谓先切琢而后可以磋磨,循序而进,工夫不辍。切磋以喻学,是就知上说止至善,讲习讨论,穷究事物之理,自浅以至深,自表以至里,直究至其极处。琢磨是就行上说止至善,谓修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直行至极处。瑟兮僩兮谓恂栗,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谓威仪,是德见于外者著。[61]
切磋琢磨,止于至善,许谦由知行两端,说明工夫所在,诚敬存乎中,尚不足有美盛德之形容,唯有达于至善,内恂栗而外威仪,融通内外,德容充溢表里。儒学有工夫、有进程,丰足饱满,由经典以入圣人之境,更有自信。《中庸章句》“诚者,天之道也”章引许谦云:
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择者,谓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谓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择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62]
以格物穷理说解经典意涵,择善而固执正是内外交养的结果。《大学章句》“所谓诚其意者”章引许谦云:
诚意只是着实为善,着实去恶。自欺是诚意之反,毋自欺是诚意工夫。二如,是诚意之实。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诚意之效,慎独,是诚意地头。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诚不诚,皆自为之。自欺者,适害己;不自慊者,徒为人。恶恶臭,好好色,人人皆实有此心,非伪也。二如字,晓学者当实
为善去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为也。[63]
以实释诚,途径直接明朗,为善去恶一出于诚,工夫纯由自己,无丝毫勉强,许谦确实掌握朱学的精神。《孟子·告子上》“操则存,舍则亡”章引许谦云:
浩然章论养气,而以心为主;此章论养心,而以气为验。曰志者气之帅,故谓以心为主。曰平旦好恶与人相近,故谓以气为验。集义固为养气之方,所以知夫义而集之者乃心也,养心固戒其梏亡。验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则气也,彼欲养而无暴,以充吾仁义之气,此欲因气之息,以养吾仁义之心。两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尝不同,而气则有在身在天之异,然未始不相为用也。[64]
这番话对心与气的关系言之甚详,养心验气,养气由心,唯有心气交养,才能仁义充盈,指出儒学极为重要的修养方法,以及朱学重要学理内容,诠释深切到位。《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章引王柏云:
“善推其所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65]
孟子开展仁义,正是善推其所为,学问在此,修养亦在此,儒学精神于此显豁,可见经典阅读的深入与精彩。当然其中也有理解偏失之处,《中庸章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章引许谦云:
程子谓不偏之谓中,固兼举动静。朱子不偏不倚,则专指未发者。[66程子兼有动静,朱熹仅言及未发之中,许氏辨别程、朱有不同的诠释重点,但对于朱熹融静于敬,涵养更密的思考,体会不深。《四书大全》载录朱熹弟子陈淳之言,云:“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可谓确而尽矣。”67朱熹取程子之说,推而及于内外动静,内涵更为周延细腻,许氏未能详究朱熹中和之悟的进程[68,观察并不深入。《大学章句》“物格而后知至”章引许谦云: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谓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揍合将来,遂全其心而足应天下事矣。[69]
“而后”既是顺序之词,也是一种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关乎工夫进程,兹事体大。《四书大全》引朱熹之说云:
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着“而”字,则是先为此而后能为彼也。盖即物而极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无不至。吾知无不至矣,而后见善明、察恶尽,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诚。意无不诚矣,而后念虑隐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70]
格物乃是修养的关键,即物穷理,知明而意诚。就工夫而言,朱熹有深刻的思考,所谓“先为此而后能为彼”,正是强调其中顺序不可紊乱,以及学术进程的安排,此为朱学工夫论的核心。然而浙东学术贵通达,许谦对此却有一种转折性的诠释,强调“致知力行”并进,于是一物之格,诚意、正心、修身乃是同时进行,最终期许逐渐理会,全其心以应天下之事,于是工夫所在,一次到位。说法是否符合朱熹原旨,有待深入讨论,但对于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因此“终身无可行之日”的逻辑问题,遂有可以解决的方向。
(二)阐明境界所在
朱熹以一生建构四书义理,如何确立有效理解,乃是后人研究的首要之务。《中庸章句序》引许谦云:
《章句》《辑略》《或问》三书既备,然后《中庸》之书,如支体之分,骨节之解,而脉络却相贯穿通透。[71]
此一方法与黄榦强调直究原典,以《章句》为研读根本的方式不同。72黄榦标举的方法,目的在于避免淆乱,然而浙东学术重视文献,更加留意考据的趣味,取径开阔,以《章句》为本,佐以《辑略》《或问》的研读方式,有助于了解朱熹思考进程,转折之间,《中庸》义理得以显豁。有关研读方法的指引,也见于《读中庸法》引许谦云:
《中庸》《大学》二书,规模不同。《大学》纲目相维,经传明整,犹可寻求。《中庸》赞道之极,有就天言者,有就圣人言者,有就学者言者,广大精微,开阖变化,高下兼包,巨细毕举,故尤不易穷究。[73]
《大学》言纲领,《中庸》明境界,研读方式,朱熹原就有安排,其云: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74]
《中庸》标举天道、圣人,期许学者有以继之,许氏所言确实符合其中旨趣。至于《章句》《或问》相参方式,提供深入朱熹义理思考细节,《中庸或问》引方逢辰可以为例,其云:
《或问》中旧说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句,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盖谓有主张是者,而实未尝有所为耳。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直谓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二说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谓鸢鱼之飞跃,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处,勿正心,谓无勉强期必,非有心着意也。活泼泼地,是指天理呈露处,此朱子旧说之意,就鸢鱼上言。今说却就看鸢鱼之人上言,谓就费视隐,必自存其心,则道理跃如矣。朱子谓只从这里收一收,这个便在,朱子两说皆精,但前说恐人无下手处,故改从后说之实。[75]
朱熹为免蹈空入虚,前后之间,趋之于实,朱学最终精神的趋向所在,于此可见。事实上,浙东学人强调文本结构,《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章引许谦云:
此章专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细微处不合道,而于远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势必当如此。故于费隐之后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谨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则言正己不求于外。此章则言自近及远,是言凡行道皆当如是也。引《诗》本是比喻说,然于道中言治家,则次序又如此。[76]
《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费而隐”[77,循此而下,第十三章阐明以恕行之,第十四章说明正己不求于外,第十五言行道自近及远,层层而进,彼此衔接,各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申明由近而及远,日用之间,道无所不在。许氏善用文学分析手法,章旨可以据此而得。此外,比较两章之间手法,也可以了解经旨所在。《中庸章句》第三十章朱注“言天道也”引许谦云:
二十六章言圣人至诚,与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则圣人之盛大自见。此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道,自万物并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则圣人之大自见。前章则引文王之诗以结之,此章则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礼,无非形容圣人之德也。[78]
圣人与天地同道,许谦比对《中庸章句》第二十六章、三十章,同样是言天地之盛大,以见圣人之盛大,铺排方式相同,至于二十九章引《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79为结,三十章则以“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80]破题,前者为文王,后者为孔子,圣圣相承,彼此衔接。至于以孔子作结,《中庸章句大全》“仲尼祖述尧舜”章引方逢辰云: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书之末,以仲尼明之。[81]
可见文本具有内在的肌理脉络,经典意义结穴所在,揭之而出,遂能彰显结构用意。经典本身原就有圣圣相承的线索,既承继而发展,又遥接而发挥,圣道境界遂有其理据。朱熹分享经典阅读经验,言“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却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821。读经必须从章句文字的语意层面,深入于文本结构当中,推敲全篇旨趣所在。浙东学人延续朱熹思考方向,诠释更趋务实。《大学章句序》“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一句引许谦云:
规模节目,以三纲八条对言,则三纲为规模,八条为节目,谓八条即三纲中事也。独以八条言之,则平天下为规模,上七条为节目,平天下是大学之极功。然须是有上七条,节节做工夫,行至于极,然后可以平天下。[83]
以《大学》而言,三纲为规模,八目为节目,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84],两相搭配,乃是极为适切的诠释。但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延伸,离三纲而言八目,以平天下为规模,格、致、诚、正、修、齐、治为节目,不无可疑,毕竟缺乏明明德之根本,八目不免有外驰之弊。或许对于元儒而言,平治天下乃是儒者事业所在,也是儒学规模所在,儒学境界于经旨当中获得启发,外王事业也是儒学的究竟,因此寄以无限的期许。许衡留意经文结构,于是将规模与节目视为境界与进程,将三纲与八目视为两个独立文本,然而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外王事业,于此可见。
五、结语
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义理推究深微,四书成为学术核心。在宋元学术纷出之际,北山学人证明朱学价值,饶富学术发展意义。《四书大全》征引的仅是部分内容,自然无法代表全貌,然而重视工夫,强调境界,北山一系学人融通经学与理学,厘清四书文本内涵,在经典诠释当中彰显朱熹学术价值。经由北山一系学人的努力与尝试,明儒四书经注诠释体系才能完成。只可惜北山一系学人为朱学嫡子,然而承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并不明显。《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章引胡炳文云:
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极功。学者不知所向,则非有志于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则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趋向之正,造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为明道矣!真知明道,则真知尧舜以至孔孟者矣!善乎勉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85]
胡炳文乃是新安一系的学者,黄榦推崇朱熹为百世而下心领神会之人,北山一系学人经由黄榦溯源于朱熹,以身份而言更为纯粹,对于朱熹道统应有进一步的说法,但是征引情形并不明显,相关论述几乎集中于新安一系学人。元代不同宗派,不同学术系统,彼此相互竞逐,《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或许出于明成祖排除明初开国浙东学人势力的一种手段。[86]然而学术积累,北山一系学人诠释心得,终不得掩,观察征引情形,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黄榦彰显朱学,以传道为己任,以影响层面而言,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是宋元朱学传播中心,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
其二,朱熹从北山一系而深入于浙学,却也不免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倾向,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其结果,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影响愈深,也难免渐生歧见。
其三,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北山一系经说以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四书大全》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的诠释成果,对于《论语》《孟子》关注不深。
其四,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推究深微,《四书大全》征引特别留意儒学修养工夫,也关注儒学境界所在,贯串绵密,融通经学与理学的思考方式,奠定了义理开展之基础。
其五,黄榦表彰朱熹,四书、朱熹、道统三位一体,北山一系学人虽然为朱学嫡子,号为正传,然而《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而延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的,却是新安一系学者。
北山一系学人乃是传承朱学的重要学脉,也是《四书大全》建构经疏体系的重要基础,只是几经转折,分析结构、推究含义,遂有不同的思考,后世儒学重要主张,隐然已见于《四书大全》征引北山学人的言论当中。工夫期许知行并进,境界强调内圣外王,对于明代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清初经世致用之学,饶有启发作用,更可见北山一系学人深层影响。只是无可讳言,《四书大全》征引内容既多且杂,梳理不易,分析脉络,尚多疏陋,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原载《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
北宋诸儒昂然奋起,证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学发展历程中精彩的一页。濂、洛、关、闽相继而起,成就斐然,然而汇聚成果,有赖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重构经典工作[1],自此由理学入于经学,由讲论而及于经典诠释,成为儒学后续发展的重要事业,朱学传布与四书讲论,乃是一体之工作。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刘爚奏请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国学[2],理宗淳祐元年(1241)诏入学宫从祀,云:“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3]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颁《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定本。[4]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场试四书义,四书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宋代沦亡,元代继起,元朝既没,明朝接续,朝代不同,但都推崇四书,四书成为宋元以降学术核心。后人往往以政治威势来解释朱熹地位的提升,认为朱熹学术乃出于官方表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庆元党禁、局势汹汹之际,无法想象日后学脉得以延伸,学术得以拓展的情形,钱穆先生“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专以科举功令为说”[6],乃是相当深入中肯的说法。朱熹的坚持与门人后学的传播,印证义理,蓄积力量,由民间而及于官方,才是建立四书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7]南宋推崇朱熹学术,来自于既压复起,还以公道,恢复朱熹名誉;元代表彰《四书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取用乃是怀柔兼纳的手段而已,用意在于笼络士子。[8]同尊朱学,程度与用意不同,真正确立朱熹学术地位,主要来自于明朝态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旧,深有恢复传统的意义,考试以朱学为宗,已具气氛,然而贯彻帝王意志,以皇权威势整合歧异,建立朱熹为尊的经说体系,主要来自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等人纂修《四书大全》[9]。自此,朱熹成为学术宗主,四书成为后代最重要经典,《四书大全》成为明代士人成学、入仕最重要的经说依据。[10]《四书大全》的地位无可比拟,检视明儒言论,邹元标《愿学集》云:“惧学者溺于异指,令童习家学,见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图无疆之治。”[11]高攀龙《高子遗书》云:“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12]指出皇权政教一体之事实。清人陆陇其甚至直指:“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13]一学术,同风俗,明显可见政治操作的影响,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四书大全》,明代“官学化”的结果便是确立四书成为最重要经典。就经学发展而言,唐代《五经正义》整合义疏,完成经学统一,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之为“经学统一时代”[14];至于明代以《四书大全》统合元儒经说,皮氏以“积衰时代”[15]来称呼明朝经学,认为其为败坏学风的源头,立场明显矛盾。事实上,《四书大全》整合宋元四书讲论内容,一如《五经正义》统合汉魏以降的经疏成果。唐承汉魏,明继宋元,落实经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经典文本,具有同样的学术发展意义,然却深受误解!为求厘清,笔者针对《四书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核以《宋元学案》,撰成《〈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16],分析庞大征引来源,探究朱熹门人结集之后学脉、宗派而及于宗族乡里情怀不同阶段的传衍线索,得出结论:黄榦传学何基,北山一系称为朱学“嫡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具有由宋入元,巩固学脉正传的地位,也具有确立朱学内涵的意义。《四书大全》征引共计106家,其中名列《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其中征引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四书大全》建立诠释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得以溯及朱熹的关键,对于掌握义理方向深有启示。
二、北山四先生之四书学
朱熹之后,黄榦为学门领袖。[17]朱学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最为重要,他们代表了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统计朱熹门人籍贯分布,以第一传门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传门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传门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传门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传门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18]可见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朱学由福建往传浙江,影响日趋深远,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按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19]黄百家(1643~1709)按语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峯亦高弟也。双峯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20]
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成为宋元朱学传播的中心,从脉络渊源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华人,从父命师事黄榦,黄榦勉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于病革之际对弟子的期许[21]。何基撰有《中庸发挥》《大学发挥》《论语发挥》,惜皆亡佚。核其语录,云:
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敬五事则明明德也,厚八政则新民也,建皇极则止至善也;至学皇极,有休征而无咎征,有仁寿而无鄙殀,则中和位育之应,皇极之极功也。
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中《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22]
前者发挥四书义理,后者深化四书义涵,不论是扩之于外或是究之于内,皆是以四书作为学术核心,《四书章句集注》与《朱子语类》相参的路径,更是指引后世解读朱熹四书学非常重要的方向[23],无怪乎黄宗羲按语云: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犹不满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应聘讲,第恐无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则,若人者,皆不
熟读四书之故也。”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24]
何基守之既严,甚至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树立熟读四书的学门宗风,正是传自黄榦学术的证明。
何基学术传于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王柏关注四书态度不变,同样强调必须深究其内而不必旁伸于外,语录云:“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盖深求之于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25]即可为证。王柏崇信四书的立场并无改易,不过细节上显然已有不同的思考,“虽曰”一句已透露端倪。王柏重视四书经文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甚于朱熹,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中庸》当依《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庸说》二篇,以“诚明”以下别为一篇[26,相歧之处,皆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义理诠释的重点。然而王柏尝试从结构化解改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王柏有关四书类著作,有《订古中庸》《论语衍义》《论语通旨》《鲁经章句》《孟子通旨》《标注四书》等,可惜大都亡佚。重构四书文本,其实是延续朱熹思考的结果,只是背离朱熹说法,尊背注而求经,奉与违戾之间,立场不免令人疑惑。[27]
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柳贯《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云:
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语孟子考证》。[28]
补充名物,以备考证,用意在于补充而非阐释。《宋元学案》黄百家按语云:
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历时既久,思之甚深,诸多说法前后不同,甚至留有诸多待解之处,临终前为《大学》“诚意”章费心竭虑,更是人所熟知之事[30]。后人延续思考方向,尝试解决经典文本与注解诠释问题,乃是学术发展的常态。黄百家申明后人应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迹,无疑是通达而且正确的看法。金氏既守朱学之教,又发四书之义,有关四书之著作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其中《大学章句疏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皆收于《四库全书》之中。金履祥传之许谦,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矣”[31],皆是朱学核心要义,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许谦于四书亦颇有心得,黄溍云: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敷绎义理,惟务平实。每戒学者曰:“士之为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至于进修利钝,则视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舍其书,何以得其心乎?圣贤之心,尽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立言,辞约意广,读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贸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觉其意初不与己异,愈久而所得愈深,与己意合者亦大异于初矣。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约意广,深嚼有味,许谦推崇至极,由朱子而得四书义理,由四书而得见圣人,饶富义理进程,只是许谦发挥义理,并不墨守朱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33]重视四书,强调朱子,也留意缺失,补正朱注。[34]许谦有关四书著作有《中庸丛说》《大学丛说》《读四书丛说》。《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说》只是四卷残本,阮元从元板影录《论语丛说》三卷,又从吴中藏书家得元版《中庸丛说》足本二卷。[35]北山学脉由宋而及元,脉络清楚于此可见: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黄榦接续朱熹,设教讲学,推究义理,昂然挺立,成为宋元之际最重要的朱学重镇,一方面传播朱学,延伸学脉;另一方面阐释义理,开展议题,证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价值。诚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汉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于同也。[36]
以动态方式看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同之与异,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无古今,学无先后,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仆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37]。既不执拘定见,又深化朱学成果,四书遂有多元丰富之诠释内容。朱学由宋入元,由注进入疏解的阶段,学人在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辩证,不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深化,贡献良多,无怪乎明代章一阳以“正学渊源”为名,纂辑四先生著作《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38],视之为由宋及元四书学发展一个重要环节;清代戴锜亦以洙泗、濂洛、关闽、北山为一脉相承之体系,其云:
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洙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弗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歧途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干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39]
承袭濂、洛、关、闽,儒学得传,北山一脉学人地位于此可见。
三、《四书大全》征引之北山学脉
《四书大全》征引当中,名列《宋元学案》之《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征引情形如下:
征引量共计154条。北山一系学人的著作如今多数已经不传,《四书大全》征引其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朱子学发展当中,北山一脉具有衔接朱门与后学的作用,对此后人深有共识。吴师道为许谦《读四书丛说》撰序言之甚明,其云:
《读四书丛说》者,金华白云先生许君益之为其徒讲说,而其徒记之之编也。君师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师鲁斋王先生柏,从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门,北山则学于勉斋黄公,而得朱子之传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中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之后,不泯灭而就微,则泮涣而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41],对于后世建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方式,具有关键地位。明代《四书大全》援取疏解内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际朱学传布情形,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体系,未见何基言论,恐与何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42]的态度有关。至于王柏、金履祥、许谦当中,许谦征引最多,则是因为许谦为入元之后发扬朱学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学列传》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43]
许谦于元代,讲学四十载,授徒著录千余人,发扬朱学不遗余力,撰作既丰,成果斐然,成为《四书大全》重要征引对象,乃是理所当然。此外,北山一系学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欧阳玄、何梦桂(《四书通》《四书大全》皆作何梦贵)、方逢辰三人。欧阳玄,字原功,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博,列于“仁山门人”,有《圭斋文集》传世。方逢辰,字君锡,学者称蛟峰先生,学术“以格物为穷理之本,以笃行为修己之实,终身顾未尝有师承”[44,然而父亲方镕为“朱学续传”,家学渊源,同是朱学一脉:
彼亦有以颖悟为道,以卤莽灭裂为学者,其说谓:“不由阶级,不假修为。”以致知格物为支离,以躐等陵节为易简,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匪徒诬人,亦以自诬,天下未有一超径诣忽焉而圣贤者。
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学之博以积之,反之约以一之。[45]
重申格致之教,阐明穷理之功。由四书而六经,学而有序,归之于理,提供了一条有进程、有境界的儒学道路,体系俨然。至于易简之教,直接圣人,不仅是自诬,而且也诬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陆,立场至为明显。然而于学术推展,北山一脉学人彰显朱学,也有与陆学争是非的意义。何梦桂,字岩叟,学者称潜斋先生,与方逢辰为讲友,宋亡不仕,于艰困之中昂扬挺立,于家国沦亡之际慨然承传,在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具有以身体道的实践意义。[46]事实上,朱熹对于吕祖谦死后的浙东学风深有疑虑,永康功利之学、永嘉事功之学继之而起,一重实利,一重实事,然而求之于外的结果,违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为利所诱。为求厘清,朱熹特别表彰金华先儒范浚,并将《心箴》载于《孟子集注》当中,以乡贤前辈的名望对治后学驰功逐利的缺失,期许从功利之中回归于人心救赎。47可见往浙东开展乃是朱熹夙愿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学人由黄榦而继承朱学,另一方面浙东本身也有其学术传统,吕祖谦于丽泽书院和明招堂讲学,门人众多[48]。金华原就是众多学派思潮交会之地,陆学、永康学、永嘉学相互交流,深有调和色彩。《朱子语录》卷122载有朱熹之分析,其云: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而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吕祖谦兼纳博采,重史轻经,成为浙东学术的特色。然而朱熹认为根源不明,不免于关键处偏失,而重权谋,求功利的结果,则不免让人违弃仁义,最终让人误以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论语》救治偏蔽,强调在日用之际,在心念之间,高举仁义价值,坚持儒学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后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也是采取相同立场。朱熹对于浙东学风深有忧虑,于此可见。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为标题,说明朱熹于南宋尚虚、尚实学风之间,展开全方位文化论战,在南宋纷然并起的学术社群当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颇能说明朱熹学术的方向。[49]而门人黄榦往浙东传学,不仅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北山一系学人习之有验的结果,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熹学术最终得以胜出。只是学术面相更为复杂,朱学既从北山一系学人而深入于浙学,却也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诠释方式,学术既延伸又相互影响,也就无怪乎《宋元学案》黄百家一方面有“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有“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的观察,甚至于最后又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50]。黄百家出于浙学,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学于浙学发展中入于史,通于文[51],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四书义理愈加丰富,却也渐生歧见,其中矛盾,正来自于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的结果,尤其后人缺乏朱熹融铸义理、思之甚深的历程[52],各自揣想之下,于经文兴发议论,时见新意,也时有误解,甚至以纠弹朱熹说法作为个人学术成就,不仅混淆朱熹四书义理体系,也造成后人了解的困扰。此一情形,从后人论述当中可以得见。邓文原《四书通序》云:“近世为图为书者益众,大抵于先儒论著及朱子取舍之说有所未通,而遽为臆说,以衒于世。余尝以谓,昔之学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学者常患其不胜古人,求胜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53]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云:“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54]议论纷出,各立门户,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学人。“争奇取异”的结果,孰为正解,顿成经典诠释的重要问题。以朱熹为宗成为后人最终的方向,回归于朱学则成为建构诠释主轴最重要的诉求,此一主张于新安一系宗主乡贤前辈的气氛中开展[55],而于明代完成。明代四书官学化过程中,确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种整合学术的手段,也是尝试解决朱学传衍问题的途径。[56]发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书经说内容,于后人剔除歧出、化异求同的调整当中,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四书大全》申明朱熹四书体系,阐释朱熹诠释经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学术传衍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发展意义。
四、诠释转折与开展
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金履祥考证四书的内容,《四书大全》收录不多,有关名物训诂的资料,《四书大全》以张存中《四书通证》为主,原因所在,可以由其言“学者于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于《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着所出”[57]一窥端倪。考证后出转精,张存中以补其所出的角度,内容更为丰富,自然成为《四书大全》取用材料。至于王柏有关《大学》《中庸》文本结构的调整,也并未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材料当中,显然关注所在,已有不同。其次,以征引的数目分析,《四书大全》征引许谦材料,《大学》29条,《中庸》34条,《论语》22条,《孟子》33条,数目相当平均,然而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分量之悬殊,即可发觉其中有异。许谦有关《大学》《中庸》诠释成果,征引比例明显较高,如果与其他人加总计算,《大学》42条、《中庸》43条、《论语》30条、《孟子》39条,《大学》《中庸》征引比例明显偏多,至于《论语》则明显偏少。检核《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大学》《中庸》各有一卷,《论语》四卷、《孟子》四卷,共计十卷,《论语》《孟子》并无空缺,经过后人筛选拣择,《四书大全》似乎更加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诠释成果,而对于《论语》《孟子》部分关注不深。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四书进程、体系与境界的讨论,对于四书义理的兴趣,高于日用之间、事理之际的体悟。朱熹对于浙东学术曾有“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28]的针砭语,似乎也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当中。事实上,检视《四书大全》列举方式,小注以朱熹《语类》、《或问》内容为主,后文辅以弟子门人意见,最末则以“云峰胡氏”“新安陈氏”“东阳许氏”等元儒诠释作结。分析征引结构,前者可见朱熹讲论之义理方向,后者可见训诂与体例的补充,形成朱熹、门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经说体系,元儒经说部分,多数依循饶鲁、新安、北山三系为序,而许谦说法往往列于征引之末,借以阐明章旨的价值与意义。可见北山一系作为朱学由宋而及元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成为后人讨论的基础。后人赓续推究,进行更全面的四书义理思索,其中排序并非偶然。北山一系学人深化与开展之处,列举如下:
(一)推究工夫进程
训解经文为《四书大全》征引内容的大宗,收录北山一系学者意见也以此类说解最多。分析语意,也辩证义理,北山学人一脉相承,经典诠释有继承发展的现象。《大学章句》朱注“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引许谦、方逢辰云:
严密,是严厉缜密。武毅,是刚武强毅。以恂栗释瑟僩,而朱子谓恂栗者,严敬存乎中,金仁山谓所守者严密,所养者刚毅,严密是不麤疏,
武毅是不颓惰,以此展转体认,则瑟僩之义可见。
瑟是工夫细密,僩是工夫强毅,恂栗是兢兢业业。惟其兢业戒惧,所以工夫精密而强毅[59]。
金履祥分出所守所养有严密与刚毅的不同,许谦、方逢辰的诠释乃是承前发展。《孟子集注·告子上》“乡为身死而不受”章引许谦云:
三乡为身,北山先生作一读,言乡为辱身失义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为身外之物,施惠于人,而受失义之禄乎,可谓无良心矣。[60]
申明经旨,乃是引用何基说法,诠释层层累聚,于此可见。北山一系学人彰显经典旨趣,揭示其中要旨,最终往往归于修养工夫的思考。《大学章句》“《诗》云:‘瞻彼淇澳’”章引许谦云:
此节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谓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绪,谓先切琢而后可以磋磨,循序而进,工夫不辍。切磋以喻学,是就知上说止至善,讲习讨论,穷究事物之理,自浅以至深,自表以至里,直究至其极处。琢磨是就行上说止至善,谓修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直行至极处。瑟兮僩兮谓恂栗,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谓威仪,是德见于外者著。[61]
切磋琢磨,止于至善,许谦由知行两端,说明工夫所在,诚敬存乎中,尚不足有美盛德之形容,唯有达于至善,内恂栗而外威仪,融通内外,德容充溢表里。儒学有工夫、有进程,丰足饱满,由经典以入圣人之境,更有自信。《中庸章句》“诚者,天之道也”章引许谦云:
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择者,谓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谓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择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62]
以格物穷理说解经典意涵,择善而固执正是内外交养的结果。《大学章句》“所谓诚其意者”章引许谦云:
诚意只是着实为善,着实去恶。自欺是诚意之反,毋自欺是诚意工夫。二如,是诚意之实。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诚意之效,慎独,是诚意地头。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诚不诚,皆自为之。自欺者,适害己;不自慊者,徒为人。恶恶臭,好好色,人人皆实有此心,非伪也。二如字,晓学者当实
为善去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为也。[63]
以实释诚,途径直接明朗,为善去恶一出于诚,工夫纯由自己,无丝毫勉强,许谦确实掌握朱学的精神。《孟子·告子上》“操则存,舍则亡”章引许谦云:
浩然章论养气,而以心为主;此章论养心,而以气为验。曰志者气之帅,故谓以心为主。曰平旦好恶与人相近,故谓以气为验。集义固为养气之方,所以知夫义而集之者乃心也,养心固戒其梏亡。验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则气也,彼欲养而无暴,以充吾仁义之气,此欲因气之息,以养吾仁义之心。两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尝不同,而气则有在身在天之异,然未始不相为用也。[64]
这番话对心与气的关系言之甚详,养心验气,养气由心,唯有心气交养,才能仁义充盈,指出儒学极为重要的修养方法,以及朱学重要学理内容,诠释深切到位。《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章引王柏云:
“善推其所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65]
孟子开展仁义,正是善推其所为,学问在此,修养亦在此,儒学精神于此显豁,可见经典阅读的深入与精彩。当然其中也有理解偏失之处,《中庸章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章引许谦云:
程子谓不偏之谓中,固兼举动静。朱子不偏不倚,则专指未发者。[66程子兼有动静,朱熹仅言及未发之中,许氏辨别程、朱有不同的诠释重点,但对于朱熹融静于敬,涵养更密的思考,体会不深。《四书大全》载录朱熹弟子陈淳之言,云:“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可谓确而尽矣。”67朱熹取程子之说,推而及于内外动静,内涵更为周延细腻,许氏未能详究朱熹中和之悟的进程[68,观察并不深入。《大学章句》“物格而后知至”章引许谦云: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谓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揍合将来,遂全其心而足应天下事矣。[69]
“而后”既是顺序之词,也是一种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关乎工夫进程,兹事体大。《四书大全》引朱熹之说云:
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着“而”字,则是先为此而后能为彼也。盖即物而极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无不至。吾知无不至矣,而后见善明、察恶尽,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诚。意无不诚矣,而后念虑隐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70]
格物乃是修养的关键,即物穷理,知明而意诚。就工夫而言,朱熹有深刻的思考,所谓“先为此而后能为彼”,正是强调其中顺序不可紊乱,以及学术进程的安排,此为朱学工夫论的核心。然而浙东学术贵通达,许谦对此却有一种转折性的诠释,强调“致知力行”并进,于是一物之格,诚意、正心、修身乃是同时进行,最终期许逐渐理会,全其心以应天下之事,于是工夫所在,一次到位。说法是否符合朱熹原旨,有待深入讨论,但对于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因此“终身无可行之日”的逻辑问题,遂有可以解决的方向。
(二)阐明境界所在
朱熹以一生建构四书义理,如何确立有效理解,乃是后人研究的首要之务。《中庸章句序》引许谦云:
《章句》《辑略》《或问》三书既备,然后《中庸》之书,如支体之分,骨节之解,而脉络却相贯穿通透。[71]
此一方法与黄榦强调直究原典,以《章句》为研读根本的方式不同。72黄榦标举的方法,目的在于避免淆乱,然而浙东学术重视文献,更加留意考据的趣味,取径开阔,以《章句》为本,佐以《辑略》《或问》的研读方式,有助于了解朱熹思考进程,转折之间,《中庸》义理得以显豁。有关研读方法的指引,也见于《读中庸法》引许谦云:
《中庸》《大学》二书,规模不同。《大学》纲目相维,经传明整,犹可寻求。《中庸》赞道之极,有就天言者,有就圣人言者,有就学者言者,广大精微,开阖变化,高下兼包,巨细毕举,故尤不易穷究。[73]
《大学》言纲领,《中庸》明境界,研读方式,朱熹原就有安排,其云: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74]
《中庸》标举天道、圣人,期许学者有以继之,许氏所言确实符合其中旨趣。至于《章句》《或问》相参方式,提供深入朱熹义理思考细节,《中庸或问》引方逢辰可以为例,其云:
《或问》中旧说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句,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盖谓有主张是者,而实未尝有所为耳。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直谓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二说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谓鸢鱼之飞跃,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处,勿正心,谓无勉强期必,非有心着意也。活泼泼地,是指天理呈露处,此朱子旧说之意,就鸢鱼上言。今说却就看鸢鱼之人上言,谓就费视隐,必自存其心,则道理跃如矣。朱子谓只从这里收一收,这个便在,朱子两说皆精,但前说恐人无下手处,故改从后说之实。[75]
朱熹为免蹈空入虚,前后之间,趋之于实,朱学最终精神的趋向所在,于此可见。事实上,浙东学人强调文本结构,《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章引许谦云:
此章专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细微处不合道,而于远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势必当如此。故于费隐之后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谨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则言正己不求于外。此章则言自近及远,是言凡行道皆当如是也。引《诗》本是比喻说,然于道中言治家,则次序又如此。[76]
《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费而隐”[77,循此而下,第十三章阐明以恕行之,第十四章说明正己不求于外,第十五言行道自近及远,层层而进,彼此衔接,各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申明由近而及远,日用之间,道无所不在。许氏善用文学分析手法,章旨可以据此而得。此外,比较两章之间手法,也可以了解经旨所在。《中庸章句》第三十章朱注“言天道也”引许谦云:
二十六章言圣人至诚,与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则圣人之盛大自见。此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道,自万物并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则圣人之大自见。前章则引文王之诗以结之,此章则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礼,无非形容圣人之德也。[78]
圣人与天地同道,许谦比对《中庸章句》第二十六章、三十章,同样是言天地之盛大,以见圣人之盛大,铺排方式相同,至于二十九章引《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79为结,三十章则以“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80]破题,前者为文王,后者为孔子,圣圣相承,彼此衔接。至于以孔子作结,《中庸章句大全》“仲尼祖述尧舜”章引方逢辰云: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书之末,以仲尼明之。[81]
可见文本具有内在的肌理脉络,经典意义结穴所在,揭之而出,遂能彰显结构用意。经典本身原就有圣圣相承的线索,既承继而发展,又遥接而发挥,圣道境界遂有其理据。朱熹分享经典阅读经验,言“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却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821。读经必须从章句文字的语意层面,深入于文本结构当中,推敲全篇旨趣所在。浙东学人延续朱熹思考方向,诠释更趋务实。《大学章句序》“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一句引许谦云:
规模节目,以三纲八条对言,则三纲为规模,八条为节目,谓八条即三纲中事也。独以八条言之,则平天下为规模,上七条为节目,平天下是大学之极功。然须是有上七条,节节做工夫,行至于极,然后可以平天下。[83]
以《大学》而言,三纲为规模,八目为节目,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84],两相搭配,乃是极为适切的诠释。但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延伸,离三纲而言八目,以平天下为规模,格、致、诚、正、修、齐、治为节目,不无可疑,毕竟缺乏明明德之根本,八目不免有外驰之弊。或许对于元儒而言,平治天下乃是儒者事业所在,也是儒学规模所在,儒学境界于经旨当中获得启发,外王事业也是儒学的究竟,因此寄以无限的期许。许衡留意经文结构,于是将规模与节目视为境界与进程,将三纲与八目视为两个独立文本,然而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外王事业,于此可见。
五、结语
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义理推究深微,四书成为学术核心。在宋元学术纷出之际,北山学人证明朱学价值,饶富学术发展意义。《四书大全》征引的仅是部分内容,自然无法代表全貌,然而重视工夫,强调境界,北山一系学人融通经学与理学,厘清四书文本内涵,在经典诠释当中彰显朱熹学术价值。经由北山一系学人的努力与尝试,明儒四书经注诠释体系才能完成。只可惜北山一系学人为朱学嫡子,然而承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并不明显。《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章引胡炳文云:
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极功。学者不知所向,则非有志于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则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趋向之正,造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为明道矣!真知明道,则真知尧舜以至孔孟者矣!善乎勉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85]
胡炳文乃是新安一系的学者,黄榦推崇朱熹为百世而下心领神会之人,北山一系学人经由黄榦溯源于朱熹,以身份而言更为纯粹,对于朱熹道统应有进一步的说法,但是征引情形并不明显,相关论述几乎集中于新安一系学人。元代不同宗派,不同学术系统,彼此相互竞逐,《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或许出于明成祖排除明初开国浙东学人势力的一种手段。[86]然而学术积累,北山一系学人诠释心得,终不得掩,观察征引情形,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黄榦彰显朱学,以传道为己任,以影响层面而言,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是宋元朱学传播中心,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
其二,朱熹从北山一系而深入于浙学,却也不免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倾向,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其结果,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影响愈深,也难免渐生歧见。
其三,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北山一系经说以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四书大全》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的诠释成果,对于《论语》《孟子》关注不深。
其四,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推究深微,《四书大全》征引特别留意儒学修养工夫,也关注儒学境界所在,贯串绵密,融通经学与理学的思考方式,奠定了义理开展之基础。
其五,黄榦表彰朱熹,四书、朱熹、道统三位一体,北山一系学人虽然为朱学嫡子,号为正传,然而《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而延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的,却是新安一系学者。
北山一系学人乃是传承朱学的重要学脉,也是《四书大全》建构经疏体系的重要基础,只是几经转折,分析结构、推究含义,遂有不同的思考,后世儒学重要主张,隐然已见于《四书大全》征引北山学人的言论当中。工夫期许知行并进,境界强调内圣外王,对于明代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清初经世致用之学,饶有启发作用,更可见北山一系学人深层影响。只是无可讳言,《四书大全》征引内容既多且杂,梳理不易,分析脉络,尚多疏陋,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原载《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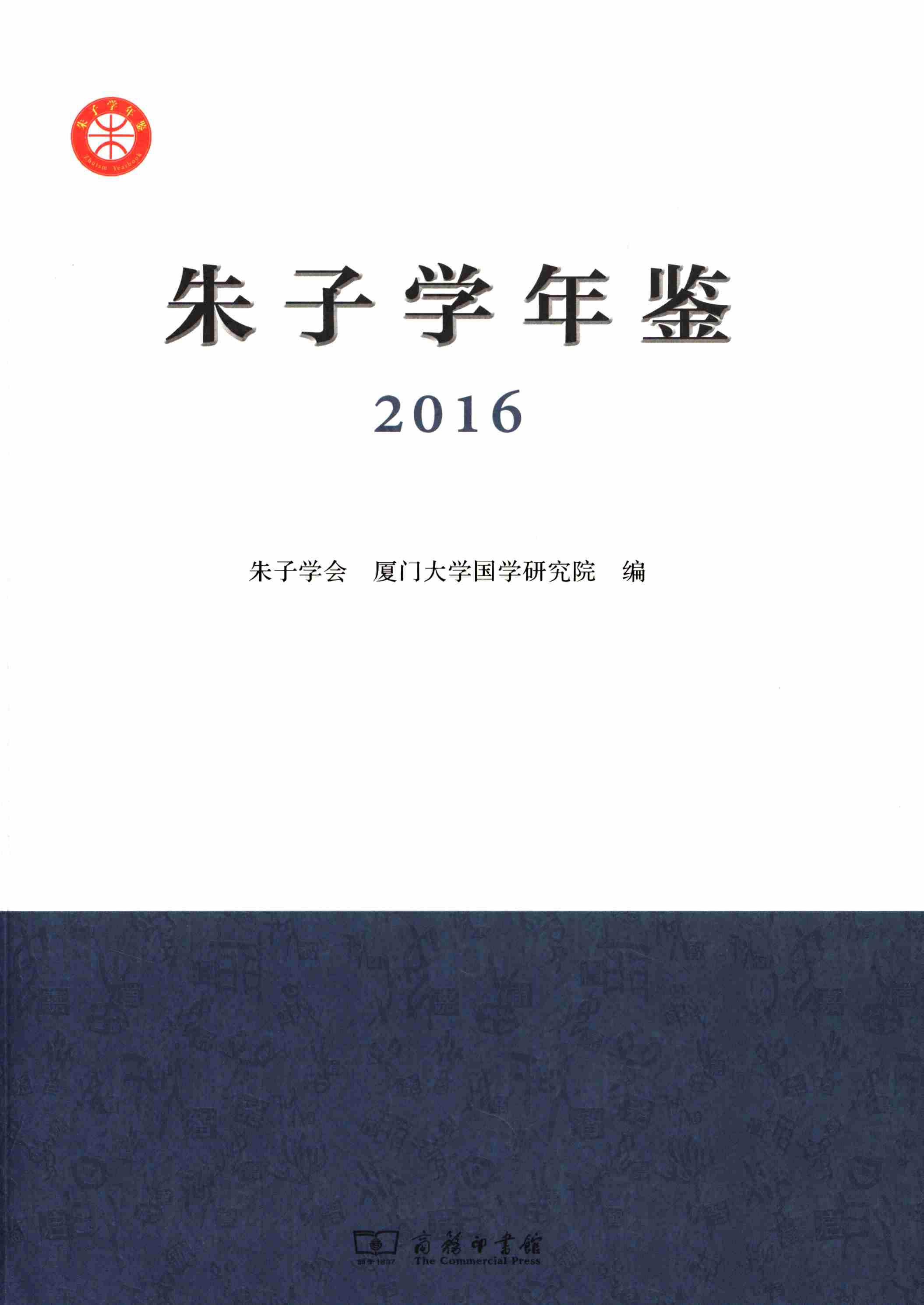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
相关人物
陈逢源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