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儒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285 |
| 颗粒名称: | 论韩儒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026-03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李退溪是韩国朝鲜朝时代的一位重要儒者,他的性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理气的问题,他更加强调了理的重要性和活动因素;关于心性情的问题,他从情的视角对四端和七情进行研究;关于践履问题,他认为敬是成圣的必要工夫。他用理气范畴来解释宇宙、人生、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他强调理气不杂,认为理是事物的极至和标准,而气是事物的形而下之器。他批评主气观点,认为理与气相分不杂的关系被忽视了。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关键词: | 李退溪 韩国 朝鲜朝 |
内容
李退溪(1501~1570)是韩国朝鲜朝时代一位继往开来,有创造性的重要儒者。他“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1]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关于理气的问题,他更加强调的是“理”的重要性和活动因素;关于心性情的问题,他突出了从“情”的视角对“四端”和“七情”的研究;关于践履问题,他竭力主张“敬”是成圣的须臾不可离的工夫。
一、“理”论
作为一名性理学者,李退溪用“理气”范畴来说明、解释宇宙、人生、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关于“理”,退溪认为“理”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又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正是由于它既重要,又难理解,古今学者对它进行不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李退溪的这一分析、判断是很准确的,不论是韩国性理学,还是中国理学,其学派分殊,大都源于对“理”的理解的差异。那么,李退溪是如何理解“理”的?他关于“理”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笔者认为,李退溪“理”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强调理气不杂。李退溪思想中的“理”以“极”的意义为其前提。如当学生问“理字之义”时,他回答说:
若从先儒造舟行水,造车行路之说仔细思量,则余皆可推也夫舟当行水,车当行路,此理也。舟而行路,车而行水,则非其理也君当仁,臣当敬,父当慈,子当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则非其理也。凡天下所当行者,理也。所不当行者,非理也。以此而推之,则理之实处可知也。
又说:
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放之无外者,此理也;敛之无内者,亦此理也;无方所、无形体,随处充足,各具一极,未见有久剩处。[2]
李退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船在水中行,车在陆上走,这是船、车之理。反之则不是船、车之理。同样,国君仁,臣子敬,父亲慈,儿子孝,这是君臣父子之理。反之则不是君臣父子之理。所以,理不分大小,没有哪样事物能超越理,也没有哪样事物不被理所包含。这说明,理没有空间,没有形体,随时随地都是完美的,它是事物的极至。“各具一极”的“极”,除了“极至”的意思之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如李退溪在《答南时甫(乙丑)》中说:极为之义,非但极至之谓,需兼标准之义,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看,方恰尽无遗意耳![3“极”除了“至极”“极至”的意义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因此,理是事物的标准。这是说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其事物,是由于理这一基准的作用或规定。理既具有极至、至极之义,又兼有标准、基准之义。这样的理,其特性是“形而上”。李退溪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形而下者,而其所具之理都是形而上者。
在性理学中,与“理”相对的概念是“气”。关于“气”,李退溪认为主要指阴阳五行之气,即“二五之气”。李退溪依据朱熹的“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来”和“阴阳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的思想,认为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变化而化生万事万物。
李退溪认为阴阳二气能够生成具有形象的万事万物,故“气”又是形而下之器,具有“形而下”的特性。
固然,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李退溪依据朱熹思想,也看到了“理”与“气”相须不分的关系。如他说:“天下无无理之气,无无气之理”。[4]他承认“理”与“气”相依不离的关系。但为了批评中国明代罗钦顺和韩国朝鲜朝徐花潭的主气观点,他认为更应强调的是“理”与“气”相分不杂的关系。
关于理气不杂的关系,李退溪指出“理”为道、为贵、为善、为形而上,“气”为器、为贱、为恶、为形而下。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然”与“所以然”的关系。
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5]
其飞其跃固是气也,而所以飞,所以跃者,乃是理也。[6]李退溪认为理气相杂的关系可以以“帅”和“卒”比喻。“理”为主导、为统帅,“气”为非主导、为兵卒。“理”与“气”有这种分殊,是因为“气”是“然”,即飞和跃是“气”的运动或发,而“气”之所以能够那样,是由于“理”的“使然”,即由于“理”统帅的结果。李退溪认为“理”与“气”的这重关系被主气学者所忽视,过于偏袒理气不分而导致认理为气或提倡理气非异物说。“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7]
李退溪指出,朱熹在《答刘叔文书》中对“理”与“气”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辩证论述并明确指出:“理与气决是二物”。但主气论者徐花潭却“终见得理字不透”,总在“气”上下工夫,最终成为朱熹所批评的“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那样的人。可见,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方面,主张理有动静。如果说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第二个特点则是主张“理有动静”。
关于“理”有无动静的问题,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主张太极(理)自身并不动静,只是所乘之机有动静。如果说到太极动静,也只是指理随气而动,朱熹讲的“天理流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并不是指理在气中运动或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理的世界在运动。这一思想朱熹后来做了进一步发展,如《语类》记载:“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卷九十四,周谟录)这是说周敦颐所谓阳动阴静并不是指太极自身能动静,所以说“非太极动静”,动静的主体是阴阳,动静的根据是理。能够运动的二气与自身不动的太极好像人跨马行走,人(太极)没有绝对运动,但有相对运动。
上述朱熹所谓的“理有动静”有两个意义。其一指理是气之动静的根据。朱熹在答郑可学书云:“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或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文集》五十六,《答郑子上》)这是说气的动静是以静之理动之理为根据的。朱熹答陈淳之问说:“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语类》九十四,陈淳录)气之动乃为其中有所以动之理为根据使然,气之静乃为其中有所以静之理为根据使然。其二,从理一看,实际只是一个理;而从分殊看,用处不同,或为动之理,或为静之理,故亦可说理有动静。综上所述,从本体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8]如朱熹曾明确地说过:“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9]明代学者薛瑄修正朱熹的“理不可以动静言”的观点,认为理自会动静。如“又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10]这是说,理(太极)既不自会动,便是死理、死人;既是死理、死人,便不能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既不足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便不能为气(阴阳)动静的根据,气(阴阳)亦不以死理(太极)为动因。这样,理何足尚,人何足贵!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承认理(太极)自会动静,理(太极)不需乘气(阴阳),气(阴阳)不需以理(太极)为动因,理气一体,理与动静一体才可。这就意味着理自会动静。
李退溪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太极生阴阳,理生气的问题,同时避免朱熹在理能否动静问题上的模糊性,他接受了薛瑄等人的太极(理)自会动静说,明确提出理有动静。如当李公浩以朱熹的理无情意、无造作,恐不能生阴阳相问时,他回答说: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
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11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引朱熹那段话的旨趣,与朱子以形而上之理(太极)是形而下之气所以动静的根据但理自身不动的思想相符合。而李退溪却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个意义上引用朱熹的话,这就与朱熹思想稍有差异。而这个差异正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发展。[2]李退溪在《答郑子中别纸》中还讲到了理自会动静的思想。如:“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13] 这里,李退溪指出,由于理动才会生出阴阳之气。他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时,也明确指出,周敦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自会动静。正是由于理的动静,才有阴阳之气的产生。主张“理自会动静”,这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李退溪提出的关于“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也正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一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情”论
李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这是因为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导致了近代朝鲜朝儒学界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形成和对立。围绕四七论而形成的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对立,堪称朝鲜朝性理学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构成了“儒学的韩国化”。这就是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论成为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探究退溪的四端七情论具有探究儒学韩国化的典型意义。
四端七情论中的“四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七情论中的“七情”,指《礼记》中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李退溪关于“四端七情”的原创性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四端”与“七情”的区别,认为“四端”与“七情”属于两个不同质的“情”范畴。二是用“理气观”对“四端七情”加以诠释。“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14]李退溪认为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经论述得很周详了。但是,用“理”和“气”来分析、阐释四端与七情,先儒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所以,以“理气”观解释“四端七情”,这确是李退溪的一个贡献。
如上所述,李退溪“理气”观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二分说,即突出理气不相杂的一面。循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四端七情”问题上,他仍然主张“四端”与“七情”的相别和相殊,即强调“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
李退溪认为情之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分,就犹如性之有“本性”与“气禀”相异一样。而性,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为什么情就不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呢?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从仁义礼智的性中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外物与身体接触而引起心中的感动,即源于外界事物而发。四端的发出,孟子说是心,而心是理与气之合,然而为什么所指是理?仁义礼智之性猝然在心中,而四者是其端绪。七情的发出,朱子说是“本来就有的当然法则”,所以并不是没有理。然而为什么所指是气?外物的到来,最易感觉并先动的,也就是形气了,而七者是其苗脉。哪有在心中是纯理,而才发出就为杂气了呢?哪有外感是形气,而能为理本体发出的呢?
可见,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所指”。李退溪认为“四端”的“所指”是“理”,“七情”的“所指”是“气”。他的这一思想在《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中讲得更明确,如他说:“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15]“七情”为“气”,“四端”为“理”。这就是四七的“所指”。而在李退溪的思想中,“理”与“气”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理”指事物的法则、本质,“气”指事物的质料(材料)。不仅如此,其性质也不同。“理”是形而上的,具有抽象、普遍的性质;“气”是形而下的,具有具体、特殊的性质。进而,李退溪将其分属于“四端”和“七情”。这就决定了“四端”与“七情”的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是其价值的区别,即“四端,皆善也。……七情,善恶未定也。”[16]他根据孟子思想,认为“四端纯善”是绝对的。由此可见,四端是抽象的情。另一方面,他讲情,并非是作为理想的、完人的圣人之情,也有常人之情,即具体的情。这样,他的四端七情就具有了互相不同的意义和特征。[17]为了进一步论证“四端”与“七情”的不同,退溪在上述引文中提到“其发各有血脉”。所谓“其发各有血脉”,也就是“所从来”的问题。
李退溪在《答奇明彦第二书》中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18]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解读李退溪的这一思想:
第一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四端可谓理之发,但此时并非无气,而气的作用是顺理(随之)而为。七情可谓气之发,但并非唯气之发,此时亦有理(乘之)。”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回答奇高峰的诘难。奇高峰主张,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应从“理气不相离”的“浑沦而言”的角度解释。所以,李退溪在说“理之发”“气之发”的同时,又补充上“气随之”“理乘之”,以表明“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而实质上,退溪的意思还是强调“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他所谓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的意思,就是“理之发,气之发”。正是由于“四端”是“理之发”,所以“自纯善无恶”,只有当“理发未遂而揜于气”时,才会流为不善。正是由于“七情”是“气之发”,所以当“气发不中而灭其理”时,就为“放而为恶”。在这里,可以从李退溪的理气不离的论述中,窥见他实质上还是从理气相分的角度来阐释“四端”与“七情”形成的根源。
第二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中的“发”“随”“乘”是三个关键性的动词。
“发”,是活动的意思。“气发”,即指气的活动,气是可以动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理发”,应解释为理的活动。如上所述,朱熹不承认理有动静,所以他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为“虚发”。而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认为理有动静。这样,在退溪的理论系统中,不论是“四端理之发”,还是“四端,理发而气随之”的“发”,都是讲的“实发”,即“理发”与“气发”的“发”,是一个意思。正是基于承认理有动静的观点,退溪竭力主张四端是理发。
“随”,是跟随、尾随,即随着的意思。李退溪讲“理发气随”,就是表明气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理发气随”的“四端”,是纯善无恶的。
“乘”,是坐、驾的意思,所以“气发理乘”就是讲,气发而理驾驭气。当气发,而理能驾驭气时,七情表现为善;当气强理弱,理驾驭不了气时,七情易流于恶。
李退溪通过“发”“随”“乘”三个关键动词,凸显了“理”的活动性、主宰性,即表明了他对“理”价值的肯定。
第三点,李退溪讲四端为理之发,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说。孟子从“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表露现象推测到仁义礼智之性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从四端皆性的意义上讲四端的“本旨”即意图。所以,李退溪讲“四端自纯善无恶”,是“理之发”,正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之上。性善说的立场作为退溪学问的立场,是先行于其方法论的前提。19
三、敬论
“敬”是理学家成圣修养的重要工夫之一,作为性理学者的李退溪固然知道这一道理。为此,退溪把“敬”作为自己学问的重要内容。《圣学十图》是退溪晚年的经典之作,可视为他学问体系的全部内容。而退溪却以“敬”之一字评价他《圣学十图》的基本内容:“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20这就是说,敬彻上彻下,贯通十图之间
李退溪的主敬思想是其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如上所述,在理气观上退溪重理轻气,视理善气恶,由此导致在性情观上,他主张“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宰之”,这就是说“四端”理发为善,而“七情”气发为恶;这就必然得出“四端,道心是也”“七情,人欲是也”的结论,进而“道心”又可称为“天理”,而“人心”则是“人欲”。要想“遏人欲,存天理”,最重要的修养工夫便是“敬”。“敬以直内为初学之急务”,“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这是说“敬”是涵养大理,遏去人欲的根本方法。
李退溪关于“敬”的理论与朱熹“居敬”“主敬”的学说,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即强调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但李退溪超过朱熹的地方是在实践、践履“敬”的真功实行方面。
本来,个人修身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始终是理学的基点和归宿。可是,在程颐,特别是在朱熹哲学中,由于更多地容纳了追求外界知识的内容,造成了格物穷理的具体活动与理学所规定给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之间的某种不一致。……因此,在格物穷理上包含着可能突破理学的倾向:一种是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的修养;一种是完全投入自然事物的研究。21可以说,日本朱子学是在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上,发展了中国朱子学而走上了一条以追求客观经验之理为目标的道路。22I而李退溪的“敬”的实践主张则是对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修养弊病的一种突破,亦是对恢复孔孟修身养性成圣传统思想的努力实践:
李退溪之所以强调突出“敬”的实践工夫,也是由朝鲜朝社会自身内部原因所决定的朝鲜朝时期“士祸”迭起,许多知识人惨遭杀害。从燕山君至明君(1495~1545)短短的五十年间,就发生了四次大士祸,被残害的读书人多达一百八十余人。李退溪的岳父权〓的父亲权柱就在“甲子士祸”(1504)中被处死,权〓遭株连被流放到济州岛,李退溪本人也受到株连,被剥夺了授予的春秋馆记事官职位。李退溪亲历了四次“士呙”,口睹了亲朋好友及学者文人的悲惨遭遇,认为惩治这一弊端的措施就是去恶从善以治心,故立志“敦圣学以立治本”。而“治本”“治心”的关键就是“敬”的修养工夫。
李退溪强调“敬”的实践工:夫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圣学十图》之中。《圣学十图》中十个图就有四个图是谈“敬”的修养工夫这就是:
《第三小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写道:“吾闻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23]李退溪认为“敬”的工夫贯彻圣学之始终,所以,《小学》所谓的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表、节度等内容就是“敬”的工夫。这些关于“敬”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大学》的明德、新民之功。
《第四大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也做了一段说明:
然非但二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盖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成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彻上彻下著工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24
这里的“非但二说”,即指小学图和大学中所引朱子关于“敬”的论说。李退溪的意思是说,从本质上二看,《圣学十图》讲的都是关于“敬”的道理。《第一太极图》和《第二西铭图》讲的是“立太极”和“立人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主“敬”的问题,故李退溪说是“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问题。而《第五白鹿洞规图》《第八心学图》《第七仁说图》《第八心学图》讲的是如何明善、如何诚身、如何盛德等身心修养问题。而这些身心修养问题,关键处是“要之,用工之要,俱不离乎一敬。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25]所以,《大学罔》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事功,都离不开敬。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也是“敬”的实践过程。
《第九敬斋箴图》告诉人们“敬”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如何行为才能做到“敬”。李退溪认为持敬就是主体心的“主一无适”。从持敬的静弗违来说,便是正其衣冠,尊其赡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从动弗违来说,便是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这就构成了动静弗违。弗违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被动接受。从持敬表交正而言,便是出门如实,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从持敬裹交正而言,便是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这就构成了表裹交正。交正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主动适应。虽然心有间、有差,但只要心敬,依照动静弗违,表裹交正的规定来体玩警醒,日用实践,就能消除有间和有差。
《第十夙兴夜寐箴图》旨在表明敬在人们行为上如何贯彻。第九图和第十图都是讲持敬行为,但二图也有不同。不同之一是第九图“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第十图“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26]这就是说,第九图是按事件而讲敬的修持工夫,而第十图是按时间而讲敬的要求训练。不同之二是第九图以“心”为核心而展开敬的工夫;而第十图则以“敬”为核心而辐射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情感。例如早晨醒来的思虑情感,省旧紬新和早晨起来的行为践履,虚明静一,然后读书应事,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从鸡鸣而寤,到昧爽乃兴,从读书对越圣贤到应事则验于为,再从日间动静循环,休养性情到晚上日暮人倦,心神归宿,都做了仔细的规定。
第九图和第十图两图结合,便明确了何时、何地、怎样做才是持敬工夫,才能做到无毫厘之差,由此,也才能达到“作圣”的境界。[27]
可见,主张持敬的实践工夫是李退溪性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他以成圣为性理学的目标,而成圣的关键是通过“敬”的修养工夫,明善诚身以至为仁、为圣,这是李退溪的终极关怀。
(原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一、“理”论
作为一名性理学者,李退溪用“理气”范畴来说明、解释宇宙、人生、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关于“理”,退溪认为“理”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又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正是由于它既重要,又难理解,古今学者对它进行不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李退溪的这一分析、判断是很准确的,不论是韩国性理学,还是中国理学,其学派分殊,大都源于对“理”的理解的差异。那么,李退溪是如何理解“理”的?他关于“理”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笔者认为,李退溪“理”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强调理气不杂。李退溪思想中的“理”以“极”的意义为其前提。如当学生问“理字之义”时,他回答说:
若从先儒造舟行水,造车行路之说仔细思量,则余皆可推也夫舟当行水,车当行路,此理也。舟而行路,车而行水,则非其理也君当仁,臣当敬,父当慈,子当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则非其理也。凡天下所当行者,理也。所不当行者,非理也。以此而推之,则理之实处可知也。
又说:
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放之无外者,此理也;敛之无内者,亦此理也;无方所、无形体,随处充足,各具一极,未见有久剩处。[2]
李退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船在水中行,车在陆上走,这是船、车之理。反之则不是船、车之理。同样,国君仁,臣子敬,父亲慈,儿子孝,这是君臣父子之理。反之则不是君臣父子之理。所以,理不分大小,没有哪样事物能超越理,也没有哪样事物不被理所包含。这说明,理没有空间,没有形体,随时随地都是完美的,它是事物的极至。“各具一极”的“极”,除了“极至”的意思之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如李退溪在《答南时甫(乙丑)》中说:极为之义,非但极至之谓,需兼标准之义,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看,方恰尽无遗意耳![3“极”除了“至极”“极至”的意义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因此,理是事物的标准。这是说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其事物,是由于理这一基准的作用或规定。理既具有极至、至极之义,又兼有标准、基准之义。这样的理,其特性是“形而上”。李退溪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形而下者,而其所具之理都是形而上者。
在性理学中,与“理”相对的概念是“气”。关于“气”,李退溪认为主要指阴阳五行之气,即“二五之气”。李退溪依据朱熹的“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来”和“阴阳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的思想,认为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变化而化生万事万物。
李退溪认为阴阳二气能够生成具有形象的万事万物,故“气”又是形而下之器,具有“形而下”的特性。
固然,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李退溪依据朱熹思想,也看到了“理”与“气”相须不分的关系。如他说:“天下无无理之气,无无气之理”。[4]他承认“理”与“气”相依不离的关系。但为了批评中国明代罗钦顺和韩国朝鲜朝徐花潭的主气观点,他认为更应强调的是“理”与“气”相分不杂的关系。
关于理气不杂的关系,李退溪指出“理”为道、为贵、为善、为形而上,“气”为器、为贱、为恶、为形而下。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然”与“所以然”的关系。
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5]
其飞其跃固是气也,而所以飞,所以跃者,乃是理也。[6]李退溪认为理气相杂的关系可以以“帅”和“卒”比喻。“理”为主导、为统帅,“气”为非主导、为兵卒。“理”与“气”有这种分殊,是因为“气”是“然”,即飞和跃是“气”的运动或发,而“气”之所以能够那样,是由于“理”的“使然”,即由于“理”统帅的结果。李退溪认为“理”与“气”的这重关系被主气学者所忽视,过于偏袒理气不分而导致认理为气或提倡理气非异物说。“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7]
李退溪指出,朱熹在《答刘叔文书》中对“理”与“气”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辩证论述并明确指出:“理与气决是二物”。但主气论者徐花潭却“终见得理字不透”,总在“气”上下工夫,最终成为朱熹所批评的“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那样的人。可见,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方面,主张理有动静。如果说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第二个特点则是主张“理有动静”。
关于“理”有无动静的问题,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主张太极(理)自身并不动静,只是所乘之机有动静。如果说到太极动静,也只是指理随气而动,朱熹讲的“天理流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并不是指理在气中运动或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理的世界在运动。这一思想朱熹后来做了进一步发展,如《语类》记载:“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卷九十四,周谟录)这是说周敦颐所谓阳动阴静并不是指太极自身能动静,所以说“非太极动静”,动静的主体是阴阳,动静的根据是理。能够运动的二气与自身不动的太极好像人跨马行走,人(太极)没有绝对运动,但有相对运动。
上述朱熹所谓的“理有动静”有两个意义。其一指理是气之动静的根据。朱熹在答郑可学书云:“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或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文集》五十六,《答郑子上》)这是说气的动静是以静之理动之理为根据的。朱熹答陈淳之问说:“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语类》九十四,陈淳录)气之动乃为其中有所以动之理为根据使然,气之静乃为其中有所以静之理为根据使然。其二,从理一看,实际只是一个理;而从分殊看,用处不同,或为动之理,或为静之理,故亦可说理有动静。综上所述,从本体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8]如朱熹曾明确地说过:“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9]明代学者薛瑄修正朱熹的“理不可以动静言”的观点,认为理自会动静。如“又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10]这是说,理(太极)既不自会动,便是死理、死人;既是死理、死人,便不能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既不足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便不能为气(阴阳)动静的根据,气(阴阳)亦不以死理(太极)为动因。这样,理何足尚,人何足贵!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承认理(太极)自会动静,理(太极)不需乘气(阴阳),气(阴阳)不需以理(太极)为动因,理气一体,理与动静一体才可。这就意味着理自会动静。
李退溪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太极生阴阳,理生气的问题,同时避免朱熹在理能否动静问题上的模糊性,他接受了薛瑄等人的太极(理)自会动静说,明确提出理有动静。如当李公浩以朱熹的理无情意、无造作,恐不能生阴阳相问时,他回答说: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
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11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引朱熹那段话的旨趣,与朱子以形而上之理(太极)是形而下之气所以动静的根据但理自身不动的思想相符合。而李退溪却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个意义上引用朱熹的话,这就与朱熹思想稍有差异。而这个差异正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发展。[2]李退溪在《答郑子中别纸》中还讲到了理自会动静的思想。如:“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13] 这里,李退溪指出,由于理动才会生出阴阳之气。他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时,也明确指出,周敦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自会动静。正是由于理的动静,才有阴阳之气的产生。主张“理自会动静”,这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李退溪提出的关于“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也正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一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情”论
李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这是因为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导致了近代朝鲜朝儒学界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形成和对立。围绕四七论而形成的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对立,堪称朝鲜朝性理学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构成了“儒学的韩国化”。这就是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论成为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探究退溪的四端七情论具有探究儒学韩国化的典型意义。
四端七情论中的“四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七情论中的“七情”,指《礼记》中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李退溪关于“四端七情”的原创性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四端”与“七情”的区别,认为“四端”与“七情”属于两个不同质的“情”范畴。二是用“理气观”对“四端七情”加以诠释。“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14]李退溪认为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经论述得很周详了。但是,用“理”和“气”来分析、阐释四端与七情,先儒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所以,以“理气”观解释“四端七情”,这确是李退溪的一个贡献。
如上所述,李退溪“理气”观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二分说,即突出理气不相杂的一面。循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四端七情”问题上,他仍然主张“四端”与“七情”的相别和相殊,即强调“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
李退溪认为情之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分,就犹如性之有“本性”与“气禀”相异一样。而性,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为什么情就不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呢?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从仁义礼智的性中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外物与身体接触而引起心中的感动,即源于外界事物而发。四端的发出,孟子说是心,而心是理与气之合,然而为什么所指是理?仁义礼智之性猝然在心中,而四者是其端绪。七情的发出,朱子说是“本来就有的当然法则”,所以并不是没有理。然而为什么所指是气?外物的到来,最易感觉并先动的,也就是形气了,而七者是其苗脉。哪有在心中是纯理,而才发出就为杂气了呢?哪有外感是形气,而能为理本体发出的呢?
可见,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所指”。李退溪认为“四端”的“所指”是“理”,“七情”的“所指”是“气”。他的这一思想在《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中讲得更明确,如他说:“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15]“七情”为“气”,“四端”为“理”。这就是四七的“所指”。而在李退溪的思想中,“理”与“气”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理”指事物的法则、本质,“气”指事物的质料(材料)。不仅如此,其性质也不同。“理”是形而上的,具有抽象、普遍的性质;“气”是形而下的,具有具体、特殊的性质。进而,李退溪将其分属于“四端”和“七情”。这就决定了“四端”与“七情”的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是其价值的区别,即“四端,皆善也。……七情,善恶未定也。”[16]他根据孟子思想,认为“四端纯善”是绝对的。由此可见,四端是抽象的情。另一方面,他讲情,并非是作为理想的、完人的圣人之情,也有常人之情,即具体的情。这样,他的四端七情就具有了互相不同的意义和特征。[17]为了进一步论证“四端”与“七情”的不同,退溪在上述引文中提到“其发各有血脉”。所谓“其发各有血脉”,也就是“所从来”的问题。
李退溪在《答奇明彦第二书》中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18]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解读李退溪的这一思想:
第一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四端可谓理之发,但此时并非无气,而气的作用是顺理(随之)而为。七情可谓气之发,但并非唯气之发,此时亦有理(乘之)。”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回答奇高峰的诘难。奇高峰主张,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应从“理气不相离”的“浑沦而言”的角度解释。所以,李退溪在说“理之发”“气之发”的同时,又补充上“气随之”“理乘之”,以表明“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而实质上,退溪的意思还是强调“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他所谓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的意思,就是“理之发,气之发”。正是由于“四端”是“理之发”,所以“自纯善无恶”,只有当“理发未遂而揜于气”时,才会流为不善。正是由于“七情”是“气之发”,所以当“气发不中而灭其理”时,就为“放而为恶”。在这里,可以从李退溪的理气不离的论述中,窥见他实质上还是从理气相分的角度来阐释“四端”与“七情”形成的根源。
第二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中的“发”“随”“乘”是三个关键性的动词。
“发”,是活动的意思。“气发”,即指气的活动,气是可以动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理发”,应解释为理的活动。如上所述,朱熹不承认理有动静,所以他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为“虚发”。而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认为理有动静。这样,在退溪的理论系统中,不论是“四端理之发”,还是“四端,理发而气随之”的“发”,都是讲的“实发”,即“理发”与“气发”的“发”,是一个意思。正是基于承认理有动静的观点,退溪竭力主张四端是理发。
“随”,是跟随、尾随,即随着的意思。李退溪讲“理发气随”,就是表明气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理发气随”的“四端”,是纯善无恶的。
“乘”,是坐、驾的意思,所以“气发理乘”就是讲,气发而理驾驭气。当气发,而理能驾驭气时,七情表现为善;当气强理弱,理驾驭不了气时,七情易流于恶。
李退溪通过“发”“随”“乘”三个关键动词,凸显了“理”的活动性、主宰性,即表明了他对“理”价值的肯定。
第三点,李退溪讲四端为理之发,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说。孟子从“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表露现象推测到仁义礼智之性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从四端皆性的意义上讲四端的“本旨”即意图。所以,李退溪讲“四端自纯善无恶”,是“理之发”,正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之上。性善说的立场作为退溪学问的立场,是先行于其方法论的前提。19
三、敬论
“敬”是理学家成圣修养的重要工夫之一,作为性理学者的李退溪固然知道这一道理。为此,退溪把“敬”作为自己学问的重要内容。《圣学十图》是退溪晚年的经典之作,可视为他学问体系的全部内容。而退溪却以“敬”之一字评价他《圣学十图》的基本内容:“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20这就是说,敬彻上彻下,贯通十图之间
李退溪的主敬思想是其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如上所述,在理气观上退溪重理轻气,视理善气恶,由此导致在性情观上,他主张“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宰之”,这就是说“四端”理发为善,而“七情”气发为恶;这就必然得出“四端,道心是也”“七情,人欲是也”的结论,进而“道心”又可称为“天理”,而“人心”则是“人欲”。要想“遏人欲,存天理”,最重要的修养工夫便是“敬”。“敬以直内为初学之急务”,“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这是说“敬”是涵养大理,遏去人欲的根本方法。
李退溪关于“敬”的理论与朱熹“居敬”“主敬”的学说,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即强调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但李退溪超过朱熹的地方是在实践、践履“敬”的真功实行方面。
本来,个人修身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始终是理学的基点和归宿。可是,在程颐,特别是在朱熹哲学中,由于更多地容纳了追求外界知识的内容,造成了格物穷理的具体活动与理学所规定给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之间的某种不一致。……因此,在格物穷理上包含着可能突破理学的倾向:一种是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的修养;一种是完全投入自然事物的研究。21可以说,日本朱子学是在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上,发展了中国朱子学而走上了一条以追求客观经验之理为目标的道路。22I而李退溪的“敬”的实践主张则是对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修养弊病的一种突破,亦是对恢复孔孟修身养性成圣传统思想的努力实践:
李退溪之所以强调突出“敬”的实践工夫,也是由朝鲜朝社会自身内部原因所决定的朝鲜朝时期“士祸”迭起,许多知识人惨遭杀害。从燕山君至明君(1495~1545)短短的五十年间,就发生了四次大士祸,被残害的读书人多达一百八十余人。李退溪的岳父权〓的父亲权柱就在“甲子士祸”(1504)中被处死,权〓遭株连被流放到济州岛,李退溪本人也受到株连,被剥夺了授予的春秋馆记事官职位。李退溪亲历了四次“士呙”,口睹了亲朋好友及学者文人的悲惨遭遇,认为惩治这一弊端的措施就是去恶从善以治心,故立志“敦圣学以立治本”。而“治本”“治心”的关键就是“敬”的修养工夫。
李退溪强调“敬”的实践工:夫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圣学十图》之中。《圣学十图》中十个图就有四个图是谈“敬”的修养工夫这就是:
《第三小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写道:“吾闻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23]李退溪认为“敬”的工夫贯彻圣学之始终,所以,《小学》所谓的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表、节度等内容就是“敬”的工夫。这些关于“敬”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大学》的明德、新民之功。
《第四大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也做了一段说明:
然非但二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盖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成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彻上彻下著工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24
这里的“非但二说”,即指小学图和大学中所引朱子关于“敬”的论说。李退溪的意思是说,从本质上二看,《圣学十图》讲的都是关于“敬”的道理。《第一太极图》和《第二西铭图》讲的是“立太极”和“立人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主“敬”的问题,故李退溪说是“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问题。而《第五白鹿洞规图》《第八心学图》《第七仁说图》《第八心学图》讲的是如何明善、如何诚身、如何盛德等身心修养问题。而这些身心修养问题,关键处是“要之,用工之要,俱不离乎一敬。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25]所以,《大学罔》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事功,都离不开敬。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也是“敬”的实践过程。
《第九敬斋箴图》告诉人们“敬”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如何行为才能做到“敬”。李退溪认为持敬就是主体心的“主一无适”。从持敬的静弗违来说,便是正其衣冠,尊其赡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从动弗违来说,便是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这就构成了动静弗违。弗违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被动接受。从持敬表交正而言,便是出门如实,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从持敬裹交正而言,便是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这就构成了表裹交正。交正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主动适应。虽然心有间、有差,但只要心敬,依照动静弗违,表裹交正的规定来体玩警醒,日用实践,就能消除有间和有差。
《第十夙兴夜寐箴图》旨在表明敬在人们行为上如何贯彻。第九图和第十图都是讲持敬行为,但二图也有不同。不同之一是第九图“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第十图“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26]这就是说,第九图是按事件而讲敬的修持工夫,而第十图是按时间而讲敬的要求训练。不同之二是第九图以“心”为核心而展开敬的工夫;而第十图则以“敬”为核心而辐射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情感。例如早晨醒来的思虑情感,省旧紬新和早晨起来的行为践履,虚明静一,然后读书应事,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从鸡鸣而寤,到昧爽乃兴,从读书对越圣贤到应事则验于为,再从日间动静循环,休养性情到晚上日暮人倦,心神归宿,都做了仔细的规定。
第九图和第十图两图结合,便明确了何时、何地、怎样做才是持敬工夫,才能做到无毫厘之差,由此,也才能达到“作圣”的境界。[27]
可见,主张持敬的实践工夫是李退溪性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他以成圣为性理学的目标,而成圣的关键是通过“敬”的修养工夫,明善诚身以至为仁、为圣,这是李退溪的终极关怀。
(原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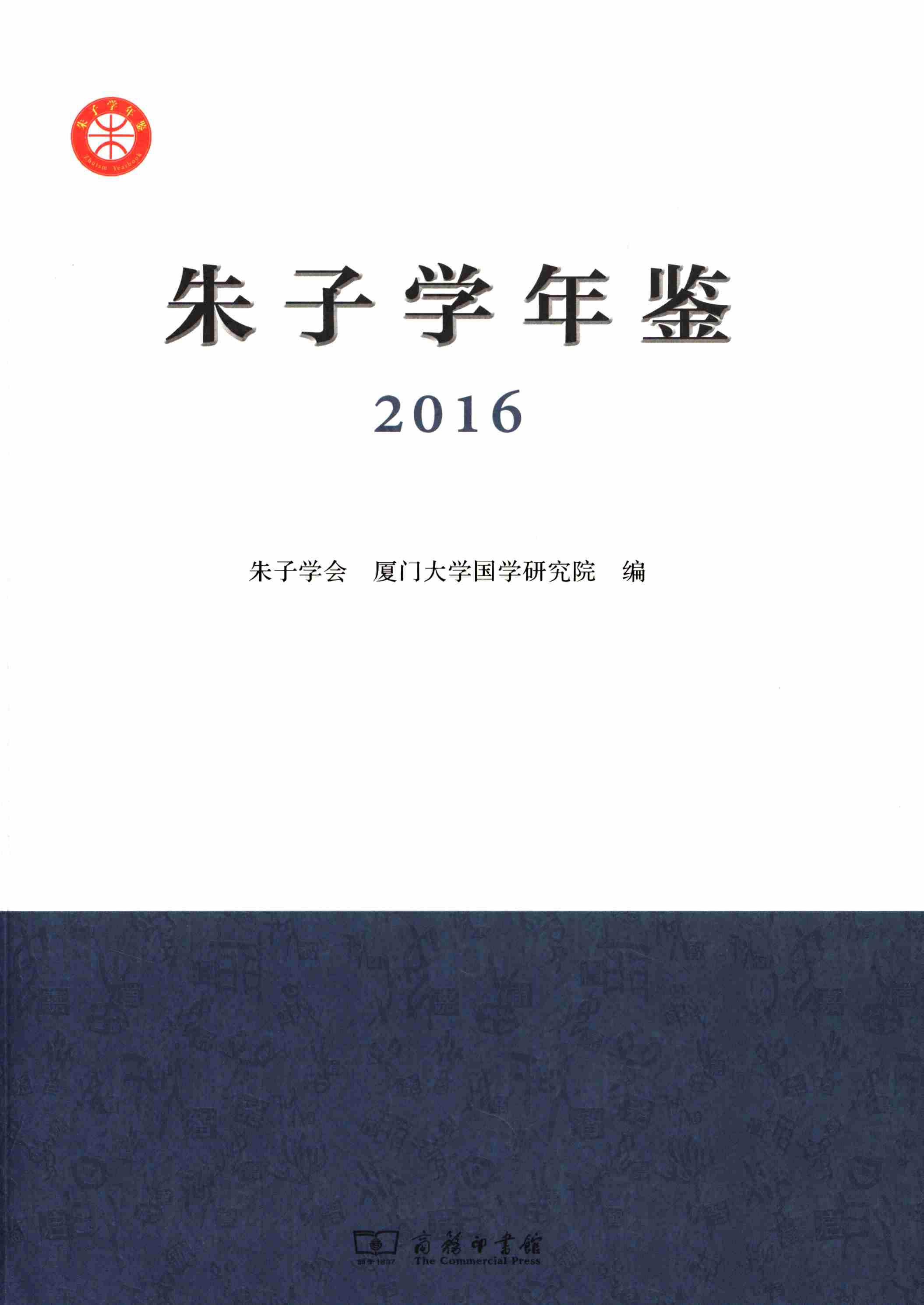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