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284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24 |
| 页码: | 025-148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朝鲜朝后期实学家对朱子学的研究和发展。通过分析这些实学家在朱子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说明了朱子学在朝鲜朝后期的重要性。 |
| 关键词: | 朝鲜朝后期 实学家 朱子学 |
内容
韩儒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
⊙李甦平
李退溪(1501~1570)是韩国朝鲜朝时代一位继往开来,有创造性的重要儒者。他“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1]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关于理气的问题,他更加强调的是“理”的重要性和活动因素;关于心性情的问题,他突出了从“情”的视角对“四端”和“七情”的研究;关于践履问题,他竭力主张“敬”是成圣的须臾不可离的工夫。
一、“理”论
作为一名性理学者,李退溪用“理气”范畴来说明、解释宇宙、人生、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关于“理”,退溪认为“理”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又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正是由于它既重要,又难理解,古今学者对它进行不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李退溪的这一分析、判断是很准确的,不论是韩国性理学,还是中国理学,其学派分殊,大都源于对“理”的理解的差异。那么,李退溪是如何理解“理”的?他关于“理”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笔者认为,李退溪“理”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强调理气不杂。李退溪思想中的“理”以“极”的意义为其前提。如当学生问“理字之义”时,他回答说:
若从先儒造舟行水,造车行路之说仔细思量,则余皆可推也夫舟当行水,车当行路,此理也。舟而行路,车而行水,则非其理也君当仁,臣当敬,父当慈,子当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则非其理也。凡天下所当行者,理也。所不当行者,非理也。以此而推之,则理之实处可知也。
又说:
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放之无外者,此理也;敛之无内者,亦此理也;无方所、无形体,随处充足,各具一极,未见有久剩处。[2]
李退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船在水中行,车在陆上走,这是船、车之理。反之则不是船、车之理。同样,国君仁,臣子敬,父亲慈,儿子孝,这是君臣父子之理。反之则不是君臣父子之理。所以,理不分大小,没有哪样事物能超越理,也没有哪样事物不被理所包含。这说明,理没有空间,没有形体,随时随地都是完美的,它是事物的极至。“各具一极”的“极”,除了“极至”的意思之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如李退溪在《答南时甫(乙丑)》中说:极为之义,非但极至之谓,需兼标准之义,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看,方恰尽无遗意耳![3“极”除了“至极”“极至”的意义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因此,理是事物的标准。这是说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其事物,是由于理这一基准的作用或规定。理既具有极至、至极之义,又兼有标准、基准之义。这样的理,其特性是“形而上”。李退溪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形而下者,而其所具之理都是形而上者。
在性理学中,与“理”相对的概念是“气”。关于“气”,李退溪认为主要指阴阳五行之气,即“二五之气”。李退溪依据朱熹的“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来”和“阴阳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的思想,认为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变化而化生万事万物。
李退溪认为阴阳二气能够生成具有形象的万事万物,故“气”又是形而下之器,具有“形而下”的特性。
固然,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李退溪依据朱熹思想,也看到了“理”与“气”相须不分的关系。如他说:“天下无无理之气,无无气之理”。[4]他承认“理”与“气”相依不离的关系。但为了批评中国明代罗钦顺和韩国朝鲜朝徐花潭的主气观点,他认为更应强调的是“理”与“气”相分不杂的关系。
关于理气不杂的关系,李退溪指出“理”为道、为贵、为善、为形而上,“气”为器、为贱、为恶、为形而下。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然”与“所以然”的关系。
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5]
其飞其跃固是气也,而所以飞,所以跃者,乃是理也。[6]李退溪认为理气相杂的关系可以以“帅”和“卒”比喻。“理”为主导、为统帅,“气”为非主导、为兵卒。“理”与“气”有这种分殊,是因为“气”是“然”,即飞和跃是“气”的运动或发,而“气”之所以能够那样,是由于“理”的“使然”,即由于“理”统帅的结果。李退溪认为“理”与“气”的这重关系被主气学者所忽视,过于偏袒理气不分而导致认理为气或提倡理气非异物说。“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7]
李退溪指出,朱熹在《答刘叔文书》中对“理”与“气”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辩证论述并明确指出:“理与气决是二物”。但主气论者徐花潭却“终见得理字不透”,总在“气”上下工夫,最终成为朱熹所批评的“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那样的人。可见,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方面,主张理有动静。如果说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第二个特点则是主张“理有动静”。
关于“理”有无动静的问题,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主张太极(理)自身并不动静,只是所乘之机有动静。如果说到太极动静,也只是指理随气而动,朱熹讲的“天理流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并不是指理在气中运动或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理的世界在运动。这一思想朱熹后来做了进一步发展,如《语类》记载:“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卷九十四,周谟录)这是说周敦颐所谓阳动阴静并不是指太极自身能动静,所以说“非太极动静”,动静的主体是阴阳,动静的根据是理。能够运动的二气与自身不动的太极好像人跨马行走,人(太极)没有绝对运动,但有相对运动。
上述朱熹所谓的“理有动静”有两个意义。其一指理是气之动静的根据。朱熹在答郑可学书云:“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或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文集》五十六,《答郑子上》)这是说气的动静是以静之理动之理为根据的。朱熹答陈淳之问说:“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语类》九十四,陈淳录)气之动乃为其中有所以动之理为根据使然,气之静乃为其中有所以静之理为根据使然。其二,从理一看,实际只是一个理;而从分殊看,用处不同,或为动之理,或为静之理,故亦可说理有动静。综上所述,从本体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8]如朱熹曾明确地说过:“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9]明代学者薛瑄修正朱熹的“理不可以动静言”的观点,认为理自会动静。如“又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10]这是说,理(太极)既不自会动,便是死理、死人;既是死理、死人,便不能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既不足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便不能为气(阴阳)动静的根据,气(阴阳)亦不以死理(太极)为动因。这样,理何足尚,人何足贵!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承认理(太极)自会动静,理(太极)不需乘气(阴阳),气(阴阳)不需以理(太极)为动因,理气一体,理与动静一体才可。这就意味着理自会动静。
李退溪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太极生阴阳,理生气的问题,同时避免朱熹在理能否动静问题上的模糊性,他接受了薛瑄等人的太极(理)自会动静说,明确提出理有动静。如当李公浩以朱熹的理无情意、无造作,恐不能生阴阳相问时,他回答说: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
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11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引朱熹那段话的旨趣,与朱子以形而上之理(太极)是形而下之气所以动静的根据但理自身不动的思想相符合。而李退溪却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个意义上引用朱熹的话,这就与朱熹思想稍有差异。而这个差异正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发展。[2]李退溪在《答郑子中别纸》中还讲到了理自会动静的思想。如:“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13] 这里,李退溪指出,由于理动才会生出阴阳之气。他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时,也明确指出,周敦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自会动静。正是由于理的动静,才有阴阳之气的产生。主张“理自会动静”,这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李退溪提出的关于“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也正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一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情”论
李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这是因为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导致了近代朝鲜朝儒学界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形成和对立。围绕四七论而形成的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对立,堪称朝鲜朝性理学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构成了“儒学的韩国化”。这就是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论成为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探究退溪的四端七情论具有探究儒学韩国化的典型意义。
四端七情论中的“四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七情论中的“七情”,指《礼记》中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李退溪关于“四端七情”的原创性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四端”与“七情”的区别,认为“四端”与“七情”属于两个不同质的“情”范畴。二是用“理气观”对“四端七情”加以诠释。“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14]李退溪认为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经论述得很周详了。但是,用“理”和“气”来分析、阐释四端与七情,先儒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所以,以“理气”观解释“四端七情”,这确是李退溪的一个贡献。
如上所述,李退溪“理气”观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二分说,即突出理气不相杂的一面。循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四端七情”问题上,他仍然主张“四端”与“七情”的相别和相殊,即强调“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
李退溪认为情之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分,就犹如性之有“本性”与“气禀”相异一样。而性,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为什么情就不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呢?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从仁义礼智的性中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外物与身体接触而引起心中的感动,即源于外界事物而发。四端的发出,孟子说是心,而心是理与气之合,然而为什么所指是理?仁义礼智之性猝然在心中,而四者是其端绪。七情的发出,朱子说是“本来就有的当然法则”,所以并不是没有理。然而为什么所指是气?外物的到来,最易感觉并先动的,也就是形气了,而七者是其苗脉。哪有在心中是纯理,而才发出就为杂气了呢?哪有外感是形气,而能为理本体发出的呢?
可见,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所指”。李退溪认为“四端”的“所指”是“理”,“七情”的“所指”是“气”。他的这一思想在《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中讲得更明确,如他说:“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15]“七情”为“气”,“四端”为“理”。这就是四七的“所指”。而在李退溪的思想中,“理”与“气”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理”指事物的法则、本质,“气”指事物的质料(材料)。不仅如此,其性质也不同。“理”是形而上的,具有抽象、普遍的性质;“气”是形而下的,具有具体、特殊的性质。进而,李退溪将其分属于“四端”和“七情”。这就决定了“四端”与“七情”的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是其价值的区别,即“四端,皆善也。……七情,善恶未定也。”[16]他根据孟子思想,认为“四端纯善”是绝对的。由此可见,四端是抽象的情。另一方面,他讲情,并非是作为理想的、完人的圣人之情,也有常人之情,即具体的情。这样,他的四端七情就具有了互相不同的意义和特征。[17]为了进一步论证“四端”与“七情”的不同,退溪在上述引文中提到“其发各有血脉”。所谓“其发各有血脉”,也就是“所从来”的问题。
李退溪在《答奇明彦第二书》中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18]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解读李退溪的这一思想:
第一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四端可谓理之发,但此时并非无气,而气的作用是顺理(随之)而为。七情可谓气之发,但并非唯气之发,此时亦有理(乘之)。”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回答奇高峰的诘难。奇高峰主张,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应从“理气不相离”的“浑沦而言”的角度解释。所以,李退溪在说“理之发”“气之发”的同时,又补充上“气随之”“理乘之”,以表明“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而实质上,退溪的意思还是强调“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他所谓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的意思,就是“理之发,气之发”。正是由于“四端”是“理之发”,所以“自纯善无恶”,只有当“理发未遂而揜于气”时,才会流为不善。正是由于“七情”是“气之发”,所以当“气发不中而灭其理”时,就为“放而为恶”。在这里,可以从李退溪的理气不离的论述中,窥见他实质上还是从理气相分的角度来阐释“四端”与“七情”形成的根源。
第二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中的“发”“随”“乘”是三个关键性的动词。
“发”,是活动的意思。“气发”,即指气的活动,气是可以动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理发”,应解释为理的活动。如上所述,朱熹不承认理有动静,所以他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为“虚发”。而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认为理有动静。这样,在退溪的理论系统中,不论是“四端理之发”,还是“四端,理发而气随之”的“发”,都是讲的“实发”,即“理发”与“气发”的“发”,是一个意思。正是基于承认理有动静的观点,退溪竭力主张四端是理发。
“随”,是跟随、尾随,即随着的意思。李退溪讲“理发气随”,就是表明气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理发气随”的“四端”,是纯善无恶的。
“乘”,是坐、驾的意思,所以“气发理乘”就是讲,气发而理驾驭气。当气发,而理能驾驭气时,七情表现为善;当气强理弱,理驾驭不了气时,七情易流于恶。
李退溪通过“发”“随”“乘”三个关键动词,凸显了“理”的活动性、主宰性,即表明了他对“理”价值的肯定。
第三点,李退溪讲四端为理之发,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说。孟子从“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表露现象推测到仁义礼智之性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从四端皆性的意义上讲四端的“本旨”即意图。所以,李退溪讲“四端自纯善无恶”,是“理之发”,正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之上。性善说的立场作为退溪学问的立场,是先行于其方法论的前提。19
三、敬论
“敬”是理学家成圣修养的重要工夫之一,作为性理学者的李退溪固然知道这一道理。为此,退溪把“敬”作为自己学问的重要内容。《圣学十图》是退溪晚年的经典之作,可视为他学问体系的全部内容。而退溪却以“敬”之一字评价他《圣学十图》的基本内容:“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20这就是说,敬彻上彻下,贯通十图之间
李退溪的主敬思想是其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如上所述,在理气观上退溪重理轻气,视理善气恶,由此导致在性情观上,他主张“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宰之”,这就是说“四端”理发为善,而“七情”气发为恶;这就必然得出“四端,道心是也”“七情,人欲是也”的结论,进而“道心”又可称为“天理”,而“人心”则是“人欲”。要想“遏人欲,存天理”,最重要的修养工夫便是“敬”。“敬以直内为初学之急务”,“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这是说“敬”是涵养大理,遏去人欲的根本方法。
李退溪关于“敬”的理论与朱熹“居敬”“主敬”的学说,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即强调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但李退溪超过朱熹的地方是在实践、践履“敬”的真功实行方面。
本来,个人修身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始终是理学的基点和归宿。可是,在程颐,特别是在朱熹哲学中,由于更多地容纳了追求外界知识的内容,造成了格物穷理的具体活动与理学所规定给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之间的某种不一致。……因此,在格物穷理上包含着可能突破理学的倾向:一种是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的修养;一种是完全投入自然事物的研究。21可以说,日本朱子学是在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上,发展了中国朱子学而走上了一条以追求客观经验之理为目标的道路。22I而李退溪的“敬”的实践主张则是对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修养弊病的一种突破,亦是对恢复孔孟修身养性成圣传统思想的努力实践:
李退溪之所以强调突出“敬”的实践工夫,也是由朝鲜朝社会自身内部原因所决定的朝鲜朝时期“士祸”迭起,许多知识人惨遭杀害。从燕山君至明君(1495~1545)短短的五十年间,就发生了四次大士祸,被残害的读书人多达一百八十余人。李退溪的岳父权〓的父亲权柱就在“甲子士祸”(1504)中被处死,权〓遭株连被流放到济州岛,李退溪本人也受到株连,被剥夺了授予的春秋馆记事官职位。李退溪亲历了四次“士呙”,口睹了亲朋好友及学者文人的悲惨遭遇,认为惩治这一弊端的措施就是去恶从善以治心,故立志“敦圣学以立治本”。而“治本”“治心”的关键就是“敬”的修养工夫。
李退溪强调“敬”的实践工:夫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圣学十图》之中。《圣学十图》中十个图就有四个图是谈“敬”的修养工夫这就是:
《第三小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写道:“吾闻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23]李退溪认为“敬”的工夫贯彻圣学之始终,所以,《小学》所谓的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表、节度等内容就是“敬”的工夫。这些关于“敬”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大学》的明德、新民之功。
《第四大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也做了一段说明:
然非但二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盖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成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彻上彻下著工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24
这里的“非但二说”,即指小学图和大学中所引朱子关于“敬”的论说。李退溪的意思是说,从本质上二看,《圣学十图》讲的都是关于“敬”的道理。《第一太极图》和《第二西铭图》讲的是“立太极”和“立人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主“敬”的问题,故李退溪说是“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问题。而《第五白鹿洞规图》《第八心学图》《第七仁说图》《第八心学图》讲的是如何明善、如何诚身、如何盛德等身心修养问题。而这些身心修养问题,关键处是“要之,用工之要,俱不离乎一敬。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25]所以,《大学罔》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事功,都离不开敬。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也是“敬”的实践过程。
《第九敬斋箴图》告诉人们“敬”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如何行为才能做到“敬”。李退溪认为持敬就是主体心的“主一无适”。从持敬的静弗违来说,便是正其衣冠,尊其赡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从动弗违来说,便是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这就构成了动静弗违。弗违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被动接受。从持敬表交正而言,便是出门如实,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从持敬裹交正而言,便是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这就构成了表裹交正。交正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主动适应。虽然心有间、有差,但只要心敬,依照动静弗违,表裹交正的规定来体玩警醒,日用实践,就能消除有间和有差。
《第十夙兴夜寐箴图》旨在表明敬在人们行为上如何贯彻。第九图和第十图都是讲持敬行为,但二图也有不同。不同之一是第九图“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第十图“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26]这就是说,第九图是按事件而讲敬的修持工夫,而第十图是按时间而讲敬的要求训练。不同之二是第九图以“心”为核心而展开敬的工夫;而第十图则以“敬”为核心而辐射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情感。例如早晨醒来的思虑情感,省旧紬新和早晨起来的行为践履,虚明静一,然后读书应事,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从鸡鸣而寤,到昧爽乃兴,从读书对越圣贤到应事则验于为,再从日间动静循环,休养性情到晚上日暮人倦,心神归宿,都做了仔细的规定。
第九图和第十图两图结合,便明确了何时、何地、怎样做才是持敬工夫,才能做到无毫厘之差,由此,也才能达到“作圣”的境界。[27]
可见,主张持敬的实践工夫是李退溪性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他以成圣为性理学的目标,而成圣的关键是通过“敬”的修养工夫,明善诚身以至为仁、为圣,这是李退溪的终极关怀。
(原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
⊙李存山
在宋代理学的“濂洛关闽”谱系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占有开山的地位,其对于朱子理学之思想体系的形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太极图说》开山地位的确立,却是经过一个历史过程的。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对这一过程的论述。
一、关于《太极图说》的争议
《太极图说》有图有说,而其图其说在理学发展史上都有争议。
首先,关于周敦颐所传“太极图”,主要是其来历的争议。南宋初,朱震(字子发)在《汉上易传表》中说:“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此后,陆九渊与朱熹辩“无极”与“太极”,指出:“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修),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抟),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至明清时期,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详加考辨,认为周敦颐所传“太极图”出自道教的《上方大洞真玄妙精品》中的“太极先天之图”或陈抟所传的“无极图”。近现代学者多有从其说者。
然而,朱熹在《太极通书后序》中说:太极图乃“(濂溪)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其根据是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所记:“(濂溪)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今人或谓“太极图易说”即是《太极图说》,但朱子在序中说“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可知朱子是把“太极图、易说、易通”理解为三本书。)
对于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认为“太极图”乃出自道教“太极先天之图”或“无极图”的考辨,今学者李申在《话说太极图》中予以否定,其根据是王卡在《道藏提要》中指出:道教的《上方大洞真玄妙精品》及《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并非唐代作品,其中提到的“真武真君”是宋真宗时所立,且其中引用了“山谷曰”(山谷即黄庭坚,与周敦颐同时),据此可证道教的“太极先天之图”当出自周敦颐所传“太极图”之后。至于黄宗炎在考辨中提到的“无极图”出于河上公、后来陈抟将之刻于华山石壁,李申也指出此说在黄宗炎之前没人说过,近于神话,并不可信。[1]
在李申提出上说之后,又有束景南、姜广辉、陈寒鸣、张其成等学者提出商榷。[2]关于“太极图”来历的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其次,关于《太极图说》的“说”,其首句除了“无极而太极”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版本,一是国史本作“自无极而为太极”,二是九江本作“无极而生太极”。朱熹把“无极而太极”解释为“无形而有理”,陆九渊则认为“无极”之说出自老子,而圣人只言“太极”,不言“无极”,《太极图说》在“太极”之上又言“无极”,是蔽于老子“有生于无”之说。朱、陆的“无极”与“太极”之辩,双方都持论甚坚,往复辩论,最后是以朱熹提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无复可望于必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六》)而告终。
对于以上争议,现代学者评价不一。笔者认为,自先秦以来儒家与道家都有“气(阴阳)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思想,秦以后儒、道两家亦共用“气(阴阳)—天地—(阴阳)五行—万物”的模式,这是儒、道两家共有的本体—宇宙论架构。两家所不同者,是道家、道教在“元气”之前还有“道生一”或“无生有”。而儒家对于这一不同的理论自觉,始于宋代的张载,即所谓“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正蒙·太和》),“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正蒙·大易》)。但是在张载之前,儒家尚未达到这种理论自觉,或者说并未将此看得有多么严重。如《易纬·乾凿度》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但其又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说,所谓“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郑玄注:“太易,无也;太极,有也。”《乾凿度》和郑玄虽然采用了道家的“无生有”之说,但其讲“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故其仍属于儒家。从儒、道两家都有“阴阳五行”的本体—宇宙论架构,而其区别主要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作为宋代理学之开山的周敦颐《太极图说》,确实在理学的思想体系建构中具有开创的地位。而辨别“太极图”的来源以及“无极”与“太极”的关系,则是后人用张载、二程以后的观点来求全于周敦颐,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释亦是以后人所求之全或他所理解的二程理本论来创造性地诠释《太极图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认为“周子《太极图说》本‘易有太极’一语,特以‘无极’二字启朱陆之争”,毛奇龄考证此图的来源以及“无极”等语不是儒书所有,其立议“不为无因”。“惟是一元化为二气,二气分为五行,而万物生息于其间,此理终古不易。儒与道共此天地,则所言之天地,儒不能异于道,道亦不能异于儒。”就此而言,毛奇龄“不论所言之是非,而但于图绘字句辨其原出于道家,所谓舍本而争末者也”。《四库》馆臣的这一评论是有见地而中肯的。本来儒、道两家共有“阴阳五行”的本体—宇宙论架构,儒家要“推天道以明人事”也不能舍此架构而不用。如果不论周敦颐在用此架构时的价值取向如何,而只是辨此图“原出于道家”,那就是“舍本而争末”。
《太极图说》讲“无极而太极”,又讲“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这里应有道家、道教的思想因素(周敦颐也确曾受到道教的影响,其诗有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几”,见《周子全书》卷十七),而周敦颐当时并不以此辨别儒、道,也就是并不将此看得有多么严重。关键是道教用“无极图”或“太极图”来讲“逆则成丹”,而周敦颐则用此图式来讲“顺而生人”,从“天道”推衍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儒家价值取向(所谓“立人极”即确立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此而言,《太极图说》在宋代理学中确实具有开创地位。
二、二程为什么不传《太极图说》
程颢、程颐早年曾受学于周敦颐,但是周、程的师生关系是常被议论的话题,而且二程不传《太极图说》,其原因更值得探讨。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近)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程氏文集》卷十一)
这段记载就隐含着周、程之关系的复杂性。“周茂叔论道”,其所论之“道”是否就是二程所创理学的“道”,二程似没有给予肯定。二程闻“周茂叔论道”的结果是“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但“未知其要”,这似可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周敦颐的“论道”还没有达其“要”;另一种是二程所学还没有达周敦颐的“论道”之“要”。从后面所说二程“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近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看,所谓“未知其要”应做前一种理解,即周敦颐的“论道”还没有“臻斯理”,而二程的理学是自得于六经,为秦汉以下所未有。这符合程颢所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氏外书》卷十二),也符合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所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氏文集》卷十一)。
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程氏遗书》卷三)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也说:程颐“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程氏遗书》附录)这里的一个细节是,二程往往称周敦颐为“周茂叔”,而不称“先生”(程颐对于胡瑗则“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朱熹则在“周茂叔”之后加上了“先生”二字。
二程从周敦颐处所得最受用的就是“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有‘吾与点也’之意”。这种境界就是儒家的以“道”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超越了自身功利的境界。有了此境界,二程“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在周敦颐的教导下,二程有了此境界,以后“孔颜乐处”“吾与点也”遂也成为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仅此一点,周敦颐是否就成为理学之开山呢?其实不然,因为宋儒讲“孔颜乐处”并不始于周敦颐,而是始于范仲淹。
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范仲淹就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锺君恨即销。”(《范文正公集》卷三)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亦教导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宋史·张载传》)。当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集·年谱》)“孔颜乐处”实即范仲淹所说的“道义之乐”,亦即儒家把“道义”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超越了对自身功利得失的计较。因为把“道义”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所以当有了“得道”之感时也就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3]
据《范文正公集·年谱》,范仲淹在景祐二年(1035)在苏州建郡学,聘请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景祐三年徙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此建郡学,“生徒浸盛”;景祐四年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在此建郡学;宝元元年(1038)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今江苏绍兴)。在这段经历中,范仲淹与为母守丧的周敦颐有一年多的时间同在润州,此期间周敦颐当受到范仲淹的影响。[4]而二程受学于周敦颐,则是在此后的庆历六年(1046)。
宋代新儒学的兴起似可分为两步:其一是儒家的价值取向的确立,此即范仲淹、周敦颐所讲的“孔颜乐处”等;其二是新儒家的“本体—宇宙论”思想体系的建构,此即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开其端。有了这第二步,周、张、二程等才成为“新儒中之新儒”。[5]
史料未载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于何时。可以肯定的是,在程颐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时,《太极图说》就已完成了。朱熹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氏遗书》附录)
这里的“皇祐二年”(1050)应为“嘉祐二年”(1057)之误[61。此时程颐二十五岁,写了长篇的《上仁宗皇帝书》,呼吁改革,表达了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内圣外王”的意识。因上此书后“不报”,程颐乃“闲游太学”,主持太学的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云:
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程氏文集》卷八)
这段话中的“天地储精”至“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是有取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此后的“其中动而七情出焉”至“故曰性其情”,则是程颐有取于胡瑗的《周易口义》。[7]
朱熹后来论及二程思想与《太极图说》的相承关系,他说:“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在朱熹举证的程氏三篇中,以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为最早。这三篇都只是节取了《太极图说》中“二五之精”以下的意思,而不讲“无极而太极……分阴分阳,两仪(天地)立焉”。《颜子所好何学论》从“天地储精”讲起,实已显露出二程之学的一个特点,即他们认为“学之道”就在既成的天地万物和人的现实世界中,这个世界虽然有“本”,但无须“穷高极远”地探讨天地之先的问题。
《程邵公墓志》是程颢在其次子去世的熙宁元年(1068)所写,有云:“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程氏文集》卷四)这里的“动静者阴阳之本”,显然也是要回避“无极”和“太极”之说。程颢的《李寺丞(仲通)墓志铭》作于熙宁七年(1074),有云:“二气交运兮,五行顺施;刚柔杂揉兮,美恶不齐;禀生之类兮,偏驳其宜;有钟粹美兮,会元之期。”(《程氏文集》卷四)这里也只言“二气”“五行”,而不言“无极”“太极”以及“是生两仪”。可见,朱熹所说“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实际上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的“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8]。这当是二程不传《太极图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熹说:“二程不言‘太极’者,用刘绚记程言,清虚一大,恐人别处走,今只说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所谓“刘绚记程言”,实为吕大临记程言,即《程氏遗书》卷二上记载二程所说:
横渠教人本只是谓世学胶固,故说一个清虚一大,只图得人稍损得没去就道理来,然而人又更别处走。今日且只道敬。
朱熹是把二程对张载之学的批评作为其不言“太极”的原因,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二程还曾说:
《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程氏遗书》卷二上)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同上)
二程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张载的《订顽》(即《西铭》),另一方面对张载超出《订顽》而讲“太虚即气”(“清虚一大”)等有所批评。张载的《订顽》讲“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在二程看来,已经表达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故云“意极完备”,“乃备言此体”,如果超出了《订顽》,那就是“恐于道无补”的“穷高极远”,“人又更别处走”。
值得注意的是,《订顽》从“乾称父,坤称母”讲起,这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不讲“无极而太极”,从“天地储精”讲起,是一致的。二程对张载之学的批评,可能也正是二程对《太极图说》的不满意之处。当然更可能反过来说,正因为二程对《太极图说》讲“无极而太极”不以为然,所以二程对张载讲“清虚一大”也有所批评。
二程不讲“无极而太极……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对《易传·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也予以回避。但是二程对《系辞》中的“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以及“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则多所发挥[9],这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从“天地储精”讲起也是一致的。
二程不言“太极”的原因,也就是二程不传《太极图说》的原因。朱熹说:
《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及“东见录”中论横渠“清虚一大”之说,“使人向别处走,不若且只道敬”,则其微意亦可见矣。若《西铭》则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远,于学者之用为尤切,非若此书详于天而略于人,有不可以骤而语者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
朱熹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不得已而作”,此“不得已”意谓“道体”幽微难言而又不得不言。其实,二程之所以不传《太极图说》,并非弟子中“未有能受之者”,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二程主张“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若讲“天道”则从“天地设位”或“天地储精”讲起就可以了,而不必“穷高极远”地讲“无极而太极……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三、北宋以后周、张著作的流传
北宋以后,在朱熹的学术成长时期,二程洛学主要分流为由杨时所传的“道南学派”和由胡安国所传的“湖湘学派”。朱熹在十四五岁时就曾读二程和张载“两家之书”10],亦曾习禅学,自二十四岁后受教于杨时的二传李侗,“李先生极言其(禅学)不是”,乃专心读“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一〇四)。在师事李侗之前,朱熹亦曾师事胡宪(胡安国从子),故亦较早受到湖湘学派的影响。
杨时最初对张载的《西铭》提出批评,后得到程颐的纠正(参见《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除《西铭》外,杨时及其所传道南学派对张载的《正蒙》持排斥态度,而胡安国及其所传湖湘学派则肯定《正蒙》。朱熹在受教于李侗时,“尝看《正蒙》,李甚不许”,“李先生云:横渠说不须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费力”(《朱子语类》卷一〇三)。道南学派的这种态度,类似于二程从“先识仁”的角度批评张载之学。而湖湘学派则对濂学和关学都持开放态度,这与胡安国及其季子胡宏同程门弟子侯仲良有过密切的接触有关。
侯仲良,字师圣,《伊洛渊源录》谓其“河东人,二先生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皆出衡山胡氏”。又载其遗事,“或曰:江陵有侯师圣者,初从伊川,未悟,乃策杖访濂溪。濂溪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伊川亦讶其不凡,曰:‘非从濂溪来耶?’师圣后游荆门,胡文定留与为邻终焉。”朱熹辨别此遗事不实:“濂溪卒于熙宁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间尚在。其题上蔡谢公手帖,犹云显道虽与予为同门友,然视予为后生。则其年辈不与濂溪相接,明矣。”(《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朱熹此说可商榷,周敦颐卒于熙宁六年(1073),此距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有五十余年,若侯仲良在二十岁上下见晚年的周敦颐,不是不可能的。
《伊洛渊源录》又载胡安国的《与杨大谏书》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门溃卒甲马之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滨,今已两年。其安于羁苦,守节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穷;商略时事,则纤微皆察。国势安危,民情休戚,凡务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晓也。方值艰难之时,而使此辈人老身贫贱,亦可慨矣。”(同上)侯仲良自兵乱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滨”,当即在靖康、建炎之间,其“游荆门,胡文定留与为邻终焉”。正是在这一时期,胡宏拜侯仲良为师。
胡宏在《题吕与叔中庸解》一文中说:“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山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有张焘者,携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师圣笑曰:‘何传之误,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师圣又夫子犹子夫也。师圣少孤,养于夫子家,至于成立。两夫子之属纩,皆在其左右。其从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其为人守道义,重然诺,言不妄,可信。”(《五峰集》卷三)由此可知,侯仲良为二程之舅的孙子,亦二程的侄女婿,他从小养于二程家,是跟从二程最久的弟子。依此关系,其“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当不是虚言。
胡安国、胡宏与侯仲良的密切接触至少有两年之久,湖湘学派对于“伊洛渊源”的认识当深受侯仲良的影响。侯仲良早年曾拜访过周敦颐,“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这对于北宋后濂溪著作的流传实具有关键意义。现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最早即出自侯仲良,而最早为其作“序”的就是胡宏。在胡宏作“序”的《通书》后,有祁宽写的《通书后跋》:
《通书》即其(周敦颐)所著也,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得之于高,后得之于朱;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传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周子全书》卷十一)
此“跋”作于绍兴甲子(1144),当时朱熹十四岁。祁宽是尹焞弟子,他先得《通书》于侯仲良所传之高元举,后得之于朱子发(震),又后来在尹焞门下得其所藏。侯氏和尹氏所传《通书》在卷末都有《太极图说》,而祁宽在九江周敦颐家所得旧本没有《太极图说》。“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或云”很可能出自侯仲良(若出自尹焞,则祁宽当直书其师之名)。尹焞是程颐晚年弟子,他所藏《通书》及《太极图说》乃“得之程氏”。但二程和尹焞等一直没有将《太极图说》示人,若无侯仲良所传,则朱震不可能于绍兴五年(1135)在所上《进周易表》中包括《太极图说》,而尹焞也仍可能将《通书》及《太极图说》藏不示人。倘若真如此,那么《太极图说》就可能湮没不闻,而朱熹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伊洛渊源”的开山之作。
侯仲良“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皆出衡山胡氏”。胡宏早年还编有《程氏雅言》,现传《五峰集》中有胡宏所作《程子雅言前序》和《后序》,这两篇序文不仅高度肯定了二程接续孟子以后失传的儒家道统,而且将其与王安石、苏轼和欧阳修之学做比较,认为王、苏、欧阳之学各有所偏,只有“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实生之,当五百余岁之数,禀真元之会,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五峰集》卷三《程子雅言后序》)。胡宏辨别北宋各学派的不同特点,他要继承和发扬二程的洛学,这是十分明确的。不仅如此,胡宏还最早提出了始自濂溪的道学(理学)谱系,这对于朱熹有重要的影响。其《周子通书序》云:
《通书》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五峰集》卷三)
这篇序文明确了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的地位,高度评价周敦颐之功“盖在孔孟之间”,又说《通书》“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这为此后朱熹最终确立周敦颐的理学之开山地位奠定了基础。
胡宏不仅表彰周敦颐之学,而且表彰邵雍和张载之学,从而提出了“北宋五子”的道学谱系。他在《横渠正蒙序》中说:
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先生名载,字子厚……与二程子为至交。知礼成性,道义之出,粹然有光,关中学者尊之,信如见夫子而亲炙之也。……著书数万言,极天地阴阳之本,穷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说而正人心,故自号其书曰《正蒙》。其志大,其虑深且远矣。(《五峰集》卷三)
胡宏在这篇序中将周、邵、二程和张载并列,此即“北宋五子”的谱系,亦即朱熹所编《伊洛渊源录》的谱系。据朱熹所说,《伊洛渊源录》中有邵雍是“书坊自增耳”(《语类》卷六十),但这也正说明胡宏提出的这一谱系的影响之大,朱熹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只是在《近思录》中排除了邵雍)。
胡宏作《横渠正蒙序》的时间大约在作《周子通书序》稍后。湖湘学派重视《正蒙》,自胡安国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著录“《正蒙》书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亦著录“《正蒙》书十卷”,解题云:“崇文校书长安张载子厚撰,凡十九篇……又有待制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按,晁、陈两书所录“《正蒙》书十卷”,当即胡宏在《横渠正蒙序》中所说“今就其编,剔摘为内书五卷、外书五卷”的合编。胡安国所传的《正蒙》一卷,可能是其选编的《正蒙》语录。概言之,《正蒙》在南宋初期的流传,亦如《通书》及《太极图说》的流传,与胡氏父子有密切的关系。
四、朱子集“濂洛关闽”之大成
朱熹说:“熹自十四五时得(二程和张载)两家之书读之”;又说:“熹自蚤岁既幸得其(周敦颐)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按,朱熹十四岁时即祁宽写《通书后跋》的绍兴甲子年(1144),朱熹初见李侗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四年后乃正式受教于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将周敦颐的《通书》寄予李侗,李在回信中说:
承惠示濂溪遗文……极荷爱厚,不敢忘,不敢忘。迩书向亦曾见一二,但不曾得见全本,今乃得一观,殊慰卑抱也。……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延平答问》)
朱熹所寄《通书》,当即《太极图说》附于《通书》卷末的版本。李侗肯定《通书》,亦如他对朱熹的一贯教导,是从内心存养以观气象的角度加以肯定。
李侗于隆兴元年(1163)逝世。三年之后,朱熹有“丙戌之悟”(所谓“中和旧说”),此“悟”就是受湖湘学派的影响,认为“性”是未发,“心”是已发。在“丙戌之悟”的当年,朱熹编成《周子通书》,此为《通书》的长沙本,即依胡宏所定章次,《太极图说》仍附于末章的版本。乾道四年(1168),朱熹校订二程的《遗书》《外书》《文集》和《经说》等著作。通过对二程关于心、性、情的诸种说法进行反复思考,朱熹又有“己丑之悟”(1169,所谓“中和新说”),放弃了“中和旧说”的以心为已发的观点,而改为“心”有体有用,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心统性情”是也。朱熹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语,与横渠‘心统性情’相似。”(《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论心,惟《答吕与叔书》最后一篇为尽。而张子所谓‘心统性情’亦为切要。”(《四书或问》卷三十六)。“己丑之悟”是朱熹的思想臻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在“己丑之悟”的同年,朱熹重编周敦颐的《太极通书》。这次重编对于朱熹确立“伊洛渊源”的道学谱系和其本人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
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太极通书后序》建安本)
朱熹把《太极图说》移到《通书》各章之前,其文献依据就是潘兴嗣(清逸)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叙周敦颐著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其深意是他认识到濂溪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且二程“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如前所述,二程的《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所好何学论》实际上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中“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二程不言“无极”和“太极”,亦不言从“太极”到“两仪”的天地分化过程。而朱熹在此所谓二程“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实已把二程以及道南学派的心性理论上达于本体—宇宙论,并且把二程之“理”解释为“太极”。
从乾道六年(1170)到乾道八年,朱熹经过与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往复商榷,修改完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和《西铭解》。在《太极图说解》中,朱熹强调:
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
这是以二程的理本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阴阳”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在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中是没有的,朱熹以“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释之,对“两仪”没有明确的解释,后来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两仪是天地,与画卦两仪意思又别。……方浑沦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间放得宽阔光朗,而两仪始立。”(《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朱子语类》卷一)这与二程的理本论不讲“太极生两仪”,而多从“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讲起,是不同的。
朱熹把《太极图说》作为“伊洛渊源”的开端,使他所诠释的理本论思想更多地加进了宇宙论的内容。在《太极图说解》中,朱熹肯定了程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故在“理气先后”的问题上没有提出“理生气”或“理在气先”之说。但张栻《答朱元晦》信中有云:“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南轩集》卷二十)吕祖谦《与朱侍讲》信中也说:“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说解》……所先欲请问者,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先体后用,先显后微之说,恐当时未必有此意。”(《东莱集》别集卷七)观此可知,在朱熹的原稿中本有“体用先后”之论。朱熹在同时期写的《答杨子直》信中也说:“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11],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在改定的《太极图说解》中已无“体用先后”之论,朱熹在《答杨子直》信中也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但朱熹在《太极图说解后记》中针对“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批评说:“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观此可知,朱熹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理生气”,但在他的思想中实已内蕴了“先有此(理)而后有彼(气)”的观点。
此后,朱熹在与陆九渊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中提出:
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
所谓“在无物之前”“在阴阳之外”即已包含了“理在气先”的思想,故黄宗羲评论说:“此朱子自以理气先后之说解周子。”(《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陈来说:“朱陆之太极辩……标志着朱子理在气先思想的明确形成。”[12]朱熹晚年倾向于理对气的“逻辑在先”说,即所谓:
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子语类》卷一)
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
所谓“本无先后之可言”,是讲理气在时间上无先后;所谓“也须有先后”,是讲理的“逻辑在先”性,理终归是气的“本原”。朱熹在《答赵致道》信中说:“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朱熹的世界本原论,即是以“理”为本原的本体—宇宙论。
朱熹在作《太极图说解》的同时也完成了《西铭解》(在《西铭解》中贯彻了《太极图说解》的思想)。这两部书标志着在朱熹的思想中“伊洛渊源”道学谱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朱熹本人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乾道九年(1173),朱熹编成《伊洛渊源录》;两年之后,即淳熙二年,朱熹与吕祖谦合编成《近思录》。在《近思录》中,收入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624条语录,分为十四卷。其首卷讲“道体”,开篇就全文录入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此统率二程与张载所言的“道体”,然后又分设“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齐家、出处、治体、制度、处事、教学、警戒、辨异端、圣贤气象”等纲目。这样就把周、张、二程之学统合为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实际上也就是朱熹的思想体系,换言之,即是“濂洛关闽”的思想体系。
在编成《近思录》的两年之后,即淳熙四年(1177),朱熹又完成了他精心撰著的《论孟集注》及《论孟或问》。先此,朱熹在完成《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的乾道八年(1172)已编成《论孟精义》,此书“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解释《论语》《孟子》之“精义”。五年之后,朱熹撰成《论孟集注》。关于《精义》与《集注》的区别,钱穆先生论之曰:
至朱子四十三岁,又成《论孟精义》……此时朱子在大体上,仍是从程门上窥二程,从二程上窥孔孟。惟于程门诸儒,已渐悟其有失师旨。
至朱子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或问》成书。此时,朱子已认《精义》中说得没紧要处多,故只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门人诸家说多所摆弃。13]
所谓“朱子始自出手眼”,就是在朱熹完成了对“伊洛渊源”道学谱系的诠释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乃自出己意而作《论孟集注》。
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署为淳熙己酉(1189)作,而此两序“是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所作的序修改而来”。[14]依此说,朱熹的《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都作于淳熙初年,它们与《近思录》是同一时期的著作。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语类》卷一〇五)所谓“四子”不仅是指孔、曾、思、孟所作的《四书》,实际上还包括了朱熹为《四书》作的《集注》。在此意义上,亦可谓:“《四书集注》,乃《六经》之阶梯;而《近思录》,乃《四书集注》之阶梯。”也就是说,若要理解儒家的《六经》,乃须通过《四书集注》;而朱熹所编《近思录》,即他对周、张、二程思想的诠释,乃成为他“自出手眼”而作《四书集注》的阶梯。
《宋元学案》说朱子的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这是与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形成了“濂洛关闽”的思想体系相联系的;钱穆先生说宋代的“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15,这也是以朱子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为其主要标志的。
(原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
朱熹的社仓设计及其流变
⊙陈支平
朱熹设立社仓,是中国救荒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南宋之后,人们对于社仓的践行,大多声称源仿于朱熹的社仓之设。因此,深刻分析朱熹对社仓的设计与实践过程及其对于后世深远影响的分析,无疑有益于进一步了解朱熹关注民生的儒家情怀,以及南宋以来社仓的演变过程。
一、朱熹对于社仓的设计与实践过程
朱熹于乾道年间在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率先创立社仓,根据其后来撰写的《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的记述,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来,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
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而王公曰:“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刘侯与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请著为例。”王公报皆施行如章。
既而王公又去,直龙图阁仪真沈公度继之。刘侯与予又请曰:“粟分贮民家,于守视出纳不便,请放古法,为社仓以储之。。不过出捐一岁之息,宜可办。”沈公从之,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于是得籍坂黄氏废地,而鸠工度材焉。经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为仓三,亭一,门墙、守舍,无一不具。[1]
根据以上记载,乾道四年(1168),当地发生饥荒,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朱熹与当地的士绅刘如愚等主持乡里的发粟赈灾。经过这次赈灾的实践,朱熹意识到民间缺乏救灾储备的弊病,以及民间配合官府救灾赈济的重要性。于是,朱熹与刘如愚等一方面向当地官府建议充分发挥官府储备仓廪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策划由当地民间自行建设救荒仓库,配合官府常平义仓的米粮散敛制度,实行灾荒时期的自救活动。最终在当地官府的资助之下,“沈公从之,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经过4个月的努力,于乾道七年八月竣工,“为仓三,亭一,门墙、守舍,无一不具”,是为“社仓”。
朱熹和刘如愚等士绅所创立的崇安县开耀乡的社仓,至少在朱熹在世之年是十分成功的。根据朱熹在晚年的追述,社仓不仅较好地起到赈济灾荒的作用,而且由于管理得当、维持有术,其积谷也不断更新,时有增益。如《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载:“始予居建之崇安,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2]
淳熙八年(1181),朱熹在浙江任上的时候,适逢浙江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全力组织救灾救荒的同时,朱熹意识到储粮救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向朝廷上报自己在十年前举办社仓的经过、所定事目条款及其效应,该上奏文约有2000余字,兹摘引如下:
宣教郎、直秘阁、新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今具社仓事目如后: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保簿重行编排。其间有停藏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之人隐匿在内,仰社首队长觉察,申报尉司追捉,解县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断罪。次年三月内,将所排保簿赴乡官交纳。乡官点检,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户一口不实,即许人告,审实申县,乞行根治。如无欺弊,即将其簿纽算人口,指定米数,大人若干,小儿减半,候支贷日,将人户请米状拖对批填,监官依状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陈未接之际,预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给贷。仍乞选差本县清强官一员,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来,与乡官同共支贷。
一、申府差官讫,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远后近,一日一都。晓示人户,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阙,不得请贷。各依日限,具状。状内开说大人小儿口数。结保,每十人结为一保,递相保委。如保内逃亡之人,同保均备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仓请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队长、大保长并各赴仓识认面目,照对保簿,如无伪冒重叠,即与签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听。其日监官同乡官入仓,据状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实,别有情弊者,许人告首,随事施行。其余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给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斗,每桶受米五省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监官、乡官人从,逐厅只许两人入中门,其余并在门外,不得近前挨拶,挽夺人户所请米斛。如违,许被扰人当厅告覆,重作施行。
一、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官米,即开两仓,存留一仓。若遇饥歉,则开第三仓,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民,庶几丰荒赈贷有节。
一、人户所贷官米,至冬纳还。不得过十一月下旬。先于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将带吏斗前来公共受纳,两平交量。旧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虑仓敖折阅,无所从出,每石量收三升,准备折阅及支吏斗等人饭米。其米正行附历收支。
一、申府差官讫,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纳。先近后远,一日一都。仰社首、队长告报保头,保头告报人户,递相纠率,造一色干硬糙米,具状,同保共为一状,未足不得交纳。如保内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备纳足。赴仓交纳。监官、乡官、吏斗等人至日赴仓受纳,不得妄有阻节。及过数多取。其余并依给米约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贷日不可差换。
一、收支米讫,逐日转上本县所给印历。事毕日,具总数申府县照会。
一、每遇支散交纳日,本县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仓算交司一名,仓子两名。每名日支饭米一斗,约半月。发遣裹足米二石,共计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贴书一名,贴斗一名,各日支饭米一斗,约半月。发遣裹足米六斗,共计四石二斗。县官人从七名,乡官人从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饭米五升,十日。共计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计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两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盖墙并买蒿荐、修补仓廒约米九石,通计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社仓支贷交收米斛,合系社首、保正副告报队长、保长,队长、保长告报人户。如阙队长,许人户就社仓陈说,告报社首,依公差补。如阙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书锁钥,乡官公共分掌。其大项收支,须监监官签押。其余零碎出纳,即委乡官公共掌管,务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别生奸弊。
一、如遇丰年,人户不愿请贷,至七八月而产户愿请者听。
一、仓内屋宇什物仰守仓人常切照管,不得毁损及借出他用。如有损失,乡官点检,勒守藏人备偿。如些小损坏,逐时修整。大段改造,临时具因依申府,乞拨米斛。
具位朱熹奏节文:一、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其法可以推广,行之他处。欲望圣慈行下诸路州军,晓谕人户,有愿置立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付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随宜立约,实为久远之计。其建宁府社仓见行事目谨录一道进呈,伏望圣慈详察,特赐施行。3]朱熹关于社仓的上奏文很快就得到朝廷的批复,准予施行天下。《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九十九附有朝廷“敕命”云:
行在尚书户部准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饬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户部状,准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书省送到宣教郎、新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同共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窃谓其法可以推广,行之他处。而法令无文,人情难强。妄意欲乞圣慈特依义役体例,行下诸路州军,晓谕人户,有愿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与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计。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则亦不至搔扰。”[4]
为此,朝廷户部还规定了比较详细的常平仓、义仓存米的敛散办法:
本部今检准绍兴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项,诸州常平钱谷及场务钱不足,申提举司,通一路之数移用,仍听互相兑便支拨。诸义仓附常平仓监专兼管,敖屋以转运司仓充其积藏,而应兑换者准常平法。诸义仓计夏秋正税,每一斗别纳五合。同正税为一钞,不收头子、脚乘钱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仓。即正税不及一斗,并本户放税二分以上,及孤贫不济者,免纳诸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县遇灾伤,当职官体量,自第四等以下阙食户给散。若放税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给。并预申提举司审度,行讫奏。诸灾伤计一县放税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户乏种食者,虽旧有欠阁,不以月分,听结保贷借。即谷不堪充种子者,纽直以钱,各成贯石,给限一年,随税纳,仍免息。……如愿依上件施行,仰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有行义者具状赴本州县自陈,量于义仓米内支拨。其敛散之事,与本乡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并不须干预抑勒。[5]
综合以上朱熹的上奏文及朝廷的饬命文,大体可以知道朱熹所倡导的社仓是一种官府与民间协作运行的粮食救荒形式。民间出资在自己的乡里建造社仓,而官府从常平义仓中拨借米谷给社仓,或借出钱文给社仓籴买米谷,从而改变以往常平仓米、义仓米只能赈济州县城郭附近灾民的被动局面,而把常平米向穷乡僻壤散发,惠及全境的贫困百姓。社仓根据春夏借出、秋冬纳还的原则,向需要借贷的乡民接济度荒的粮食。如此则官粮、官钱不亏,民间也可比较平稳地度过青黄不接的时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熹所设计的社仓还有着一系列相互配套的事目条款。
首先,为了防止舞弊行为,民间在设立社仓的同时,必须先清理当地的户口,重新编排保簿。“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保簿重行编排。其间有停藏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之人隐匿在内,仰社首队长觉察,申报尉司追捉,解县根究……次年三月内,将所排保簿赴乡官交纳。乡官点检,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户一口不实,即许人告,审实申县,乞行根治。”在落实了当地的实际户口之后,才能指定米数,结算人口,实施赈给。
其次,对于管理社仓的人选,即社首、保正副、队长、大保长等,必须差使“本乡土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敛散之事,与本乡耆老公共措置”。也就是说,主持社仓的人选,基本上是以乡居的士绅为主,加上一些在乡里有声望的“有行义者”。如朱熹和刘如愚主持崇安县开耀乡的社仓建造之后,朱熹所推荐的管理社仓人选大多是刘如愚的族人。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说:“既成,而刘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请曰:(刘)复与得舆皆有力于是仓,而刘侯之子将仕郎琦尝佐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职郎玶亦廉平有谋,请得与并力。府以予言悉具书礼请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与讲求仓之利病,具为条约。”[6]“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7]朱熹认为社仓管理人选关系到社仓及救荒事宜能否得以成功的大事,必须有德高望重的士人们主持。他在《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中说:“常平者,独其法令簿书筦钥之仅存耳,是何也?盖无人以守之,则法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于所谓社仓者,聚可食之物于乡井荒闲之处,而主之不以任职之吏,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聪明仁爱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数公者,相与并心一力,以谨其出纳而杜其奸欺,则其法之难守,不待已日而见之矣。”[8]社首等管理人员名单的确认,最后还要经过官府审核批准,“即申尉司定差”。每次敛散社仓米谷之时,一般都有官府派下的吏员监督,“簿书锁钥,乡官公共分掌。其大项收支,须监监官签押。其余零碎出纳,即委乡官公共掌管,务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别生奸弊。”
最后,为了确保官府借出的常平义仓米谷不致损失缺额,社仓事目中还规定了米谷借出后至秋冬纳还时所应当加收的息米或耗米。“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但是如果遇到严重灾年之时,一般平民百姓交纳息米相当困难,事目又规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息米可以酌情减免,“人户所贷官米,至冬纳还……旧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虑仓敖折阅,无所从出,每石量收三升。”“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由于规定了比较合理的还纳加息条款,不仅可以基本保证官米不失,而且还有可能不断增加社仓的存谷,储蓄日丰。朱熹的五夫社仓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
从朱熹的社仓设计中可以看出,由于是官府与民间协作办理的体制,其社仓事目既考虑到官府对于社仓的监督作用,又规定了社仓的管理人选必须是当地的士绅及有行义者,两者相互配合、相互牵制;同时还兼顾到官府和民间的经济效益问题,既要使社仓发挥赈济贫困、储蓄备荒的功能,又不能让官府的常平义仓缺额亏本。朱熹的这种社仓设计,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效果与功能,难怪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历代人们的关注和效仿。这一设计充分反映了朱熹在民生理念上的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向朝廷奏请把自己的社仓模式推广于天下诸路州军时,其社仓设置之初的米谷来源,是政府的“常平仓”,但是到了户部批复时,则变成了“义仓”。南宋时期“常平仓”与“义仓”的存谷来源是有区别的。根据李华瑞的研究,常平仓米,“其籴本主要是留用地方上供钱支出,‘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后二三千贯,付司农司系帐。三司不问出入,委转运使并本州委幕职一员专掌其事。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9]这就是说,常平仓米事由上供财政款中截留地方使用的份钱中支用,属于政府财政预算内的开支。义仓米则不同。“义仓粮食的来源是各州属县于‘两税每石别输一斗贮之。’……义仓令主户于‘夏秋正税外每一石别纳一斗,随常赋以入。’”[10]也就是说,义仓内的米谷存储属于正税之外的附加。如此一来,朱熹原先的设计是由官府财政钱谷中出借社仓的“元本”,而到了户部的批复“饬命”中,则成为以“义仓”的名义向愿意设置社仓的乡村加收额外的税款,“诸义仓计夏秋正税,每一斗别纳五合。同正税为一钞,不收头子、脚乘钱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仓。”户部堂而皇之地把原先应属政府财政支出的常平仓米转化为加收额外税的义仓米支借给社仓,社仓赈济的重担最终试图转嫁给社仓所涵盖的一般民众。而从地方官的角度看,义仓加收社仓本米,不啻是加赋。担负加赋之名是一般地方官员比较忌讳的事情,于是大多数地方官员对于设置社仓的态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作壁上观,省得招惹麻烦。即使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多收税额总是坏事,灾害是否来临尚未可知,眼前就要多交税额,心理不好承受。由此看来,淳熙八年朝廷批准朱熹的社仓奏请推广于天下,基本上是表面文章,口惠实不惠。
二、南宋时期社仓实施的基本情况
朱熹对于宋孝宗批准自己的社仓建议,十分高兴,他在抄录朝廷饬命文之后送撰写的《跋语》中说:“往岁里中妄意此举,所以收恤隐民者,盖偶合其微指。顾以国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远及,且惧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遍下郡国,将遂得与阖宇之间含生之类均被仁圣之泽于无穷,固已不胜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积,又得上为明诏之所称扬,下为四方之所取则,抑又有荣耀焉。”11]因此,他又发动管辖之下的州县,赶紧施行,亲自写了《劝立社仓榜》,告示属下官府及民间,该榜文云:
当司恭奉圣旨,建立社仓,已行印榜,遍下管内州县劝喻。寻据绍兴府会稽县乡官、新嘉兴主簿诸葛修职名千能状,乞请官米置仓给贷。而致政张承务名宗文、新台州司户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龙游县袁承节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谷置仓给贷。当司契勘前件官员心存恻怛,惠及乡闾,出力输财,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挥具申朝廷外,须至再行劝勉,量出米谷,恭禀圣旨,建立社仓,庶几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有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再此劝喻,各请知委。12]
朱熹的社仓设计虽然于淳熙八年十二月由朝廷批准向全国推广,但是其实际施行的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关于这一点,朱熹曾经多次提到。如《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载:“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社仓),因得条上其说。而孝宗皇帝不以为不可,即颁其法于四方,且诏民有慕从者听,而官府毋或与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13]《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中亦云:“始予居建之崇安,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中间蒙恩召对,辄以上闻,诏施行之,而诸道莫有应者,独闽帅赵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为能广其法于数县,然亦不能远也。”[14]
其实,朱熹所创立的社仓法虽然有朝廷予以推广的谕令,但不能在当时的各个地区施行,是与南宋的社会经济及政府财政状况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仓法是一种由官府和民间相互协作而成的救荒形式,这就需要具备两种基本条件。一是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民间有较为宽裕的粮食剩余以及储备;二是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各地官府能够在上供财政和日常财政支出之外,尚有余钱余谷来向民间出借,从而保障民间社仓的正常运转。但是在朱熹所处的时代,这两个方面都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由于宋代实行基本上“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社会诸等级对土地的占有是极为悬殊的。根据漆侠的研究,宋代经历了三次土地兼并的高潮。其中,第三次兼并高潮在南宋初年就出现了。这次兼并土地的高潮,从宫廷到民间,从临安到地方,到处兴起,官僚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州县寓官,候补等缺之余,以兼并土地为事。[115各阶级阶层对土地的占有情形为:“占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的地主阶级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其中占总人口千分之四五的大地主占田竟达百分之四五十,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过是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下。”[16
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官府册籍混乱、经界不清,一般的贫苦农民虽然占地很少,但是政府的各种赋税却大部分转嫁到他们身上,痛苦不堪。前述朱熹一直以清经界为己任,就是深刻地认识到南宋时期土地兼并对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当然,在南宋的大环境之下,朱熹的这一愿望是很难实现的。社会资源占有的严重不公平,加上南宋朝廷所管辖的地域比较狭小,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南宋时期的政府财政始终处于困难之中。“南宋是在兵荒马乱中建立起来的,又是在硝烟弥漫中被摧垮的。”兵连祸结,靡有已时。因而财政开支浩大有其客观原因,“但更加主要的是财政开支之滥施是由于南宋统治的腐败”。[17]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压力,南宋政府基本上是在两税征收中采取了压榨广大自耕农民的财政政策,两税征收大幅度地增加起来,特别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更是让平民百姓不胜其扰。
在这种一般下层百姓穷困潦倒、政府财政窘迫的困境之中,政府要实施有效的社会救助措施,就显得相当困难。宋代设有“常平仓”“义仓”等制度,原意是政府储备一定数额的余粮,在发生自然灾害等不时之需时,政府散发常平仓、义仓中的粮食,救济受灾民众。从制度上说,这类属于应急灾荒的常平仓、义仓储备粮食是“不得他用”[18]的。但是到了朱熹的时代,常平仓、义仓中的存粮,经常被官府的其他通途所挪用。朱熹为此一再上奏朝廷,谴责那些挪用常平仓米和义仓米的官员,要求朝廷予以惩治,但是朝廷深知这些常平仓米、义仓米的所谓用于“赈济”,只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因此对于朱熹的上奏文,基本上装聋作哑、不予批复。如朱熹在浙江任上,对于地方官员把常平仓米作为“官兵米”散给,相当气愤,他在《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中云:
照对臣昨据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崈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适当荒歉之后,财计匮乏,别无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于丰储仓内更给助米二万石,以济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余石,未有指拟,逐急于常平义仓米内权行借兑,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赐处分施行外,申本司照会。……去后又据衢州申,再行借兑义仓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粮米。……臣伏缘在法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违制论。……意谓朝廷必须薄行责罚,以戒后来。今乃一无所问,亦不略行戒约,即在本司,何以约束诸郡?19]
然而让朱熹更为气愤的是,上奏文呈递上去之后,擅自借兑常平仓米的官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越支越多,朱熹只好再次上呈《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义仓米状》云:
衢州沈崈一违法擅行借兑过常平义仓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下衢州,督催补还元旧窠名,及具录奏闻,乞将本州当职官略行责罚,以戒将来,未得回降。今来再据衢州沈崈一申,又于常平米内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军粮,三个月共擅借过一万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过常平米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系充官兵俸料,未曾拨还。及称目下盘量折欠米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项共计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臣照对在法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违制论……而本州略无忌惮,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窃虑必有情弊。……欲望圣慈先将衢州违法擅支常平义仓米当职官吏特行责罚,以警诸郡,为擅用常平义仓米者之戒。[20]
不仅衢州如此,婺州也是如此,经过数次支借之后,常平仓内存米仅剩7000余石,但是官员还向朝廷申请再挪2万石,竟然得到朝廷的批准。这就不单单是挪用常平仓米的问题,地方掌管财政的官员不得不东挪西借,把其他方面的开支钱谷暂时拿来应付“支遣军粮”了。朱熹在《乞降旨令婺州拨还所借常平米状》中说:
臣伏准尚书省劄子,备据知婺州钱佃奏,乞于本州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支借二万石支遣军粮。八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许支借二万石,限至岁终拨还。臣除已恭禀施行外,臣窃见义仓米在法唯充赈给,不许他用。今岁婺州诸县例皆旱伤,将来细民必致阙食。……先来本州已曾借过一万七千石,元降指挥,候秋成先次拨还,尚未还到颗粒。今来再借二万斛,止存七千余石,已是不足支遣。……欲望圣慈,特降指挥,令婺州将两次借过米三万七千石趁此秋成,尽数先行拨还,庶几可以添助赈济。[21]
这些奏请基本上没有取到朱熹所预期的效果,常平仓米、义仓米被地方官府挪作他用的情景不断发生。[22这就大大降低了常平仓、义仓原先所设计的基本功能,逐渐沦为政府应急财政的一个储备口。再加上有些地方官吏的怠政行为,加剧了常平仓、义仓的某些弊病。如有些官吏对于常平仓疏于日常管理和运作,致使常平仓内的存谷、存米腐败变质、无法食用;有些常平仓常年关闭,无人问津,无法惠济灾民。朱熹在江西任上以及福建等地,都看到了这种情景。其中,江西的情景为:
所有本军(南康军)城下常平仓见椿管口口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石二斗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月内盘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石三斗二升四合外,实管见在米七千八百三十石九斗四升一合二勺。系是乾道八年以后逐年收籴到数目,价钱不一。其米经年在敖,内有结冒陈损。兼照今年七月内,管属建昌县阙少米斛出粜,所支拨义仓米估价应接民间食用,每升计价钱一十文足。已具收报提举使衙门照会去讫。所有见管和籴米,本军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经年陈损,与受纳到人户义仓米陈损色样一同,依市价每一升估计价钱一十文足本军照得上件米系是当来委官和籴到数目,且虑亏损元价,未敢擅便出粜。23
福建的情景为:
“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24]
由于无法保障常平仓米、义仓米的充足供给支借,再加上朝廷对于社仓建议所采取的是“口惠实不惠”的敷衍态度,义仓所存米谷的责任推还给基层百姓,设置社仓,须先加赋,造成许多地方百姓对于建立社仓的意愿相当低下,许多地方官就只能对于淳熙八年推广社仓的谕令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了。因此,朱熹的社仓设计虽然得到宋孝宗的批准,推行于全国,但是并没有在当时形成行政制度上的施行。
台湾学者梁庚尧曾经广泛搜集南宋时期的社仓资料,统计出社仓建议在朱熹之后有很大发展,共有记载64处之多。“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西、湖南、四川、广南、淮南各地,可说是几乎遍布南宋各区。”但是这些社仓的出现并非主要由政府的行政制度所促成,而主要是一些地方人士和官员仰慕朱熹的道德理念所促成的。梁庚尧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各社仓的创办人,如诸葛千能、张洽、李燔、赵师夏为朱熹门人,真德秀、赵景纬为朱熹再传弟子,万镇为三传弟子,魏了瓮、李道传、李大有则为私淑朱熹之学者;其他如陆九韶为陆九渊的家兄,和朱熹是时相论学的好友,丰有俊为陆九渊门人,刘宰为张栻再传弟子,潘景宪为吕祖谦门人,也都是理学同道。可知社仓的推广,朱熹门人和理学同道出力甚多。”[25]而从社仓的地理分布上看,以朱熹长期讲学的福建以及朱熹的过化地区最多,仅福建就有11个州县施行,几占南宋各地社仓的五分之一。因此,从梁庚尧的统计数字中,我们看不出当时政府在行政制度上对于社仓施行的保证与推行,南宋社仓的设置,基本上是个案性的、道德性的传播。上面引述朱熹本人对于当时社仓难于推广的叹息,即所谓“至今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今几三十年矣……诏施行之,而诸道莫有应者……然亦不能远也”,可能更为接近南宋社仓的基本事实。
当然,社仓难以在南宋推广,归根到底在于社会经济的不振与政府财政的困窘。南宋朝廷即使有意愿从行政制度上在全国推行社仓,也只能通过“义仓”加税的办法来施行。然而这种加税的办法,恰恰又阻碍了从行政制度上推行社仓的可能性。不仅南宋如此,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凡是救荒政策实施得比较得力的年代,基本上是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如康雍乾时期号称“盛世”,也是社仓等比较繁盛的时期。[26]反之,到了清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社仓之举也就逐渐沦为名存实亡的状态。
三、朱熹社仓的影响与流变以及清代社仓的繁盛
朱熹所提倡的社仓,虽然在南宋时期未能得到较为广泛的施行,但是其历史影响却是十分深远。迄至明清时期,凡举办置仓救荒之策,大多要提到朱熹的社仓设计。特别是到了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国家财政相对宽裕,民间也往往有所盈余,在三位皇帝的推动下,朱熹所设计的社仓模式得到了空前发展。可以说,朱熹的社仓设计未能在南宋时期得到有效的施行,在明代也是时有时无,无法形成整体性的社仓氛围。唯有在清代的康雍乾时期才得到比较全面的践行。然而,如果进一步对朱熹设计的社仓制度与明清时期的社仓实施情况做更深入的比较,还是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
如上所述,朱熹在崇安县开耀乡设置五夫里社仓时,其米谷是从官府的常平仓或义仓中支借出来的,淳熙八年朱熹向朝廷奏请向天下推广社仓设置时,提出了以向官府支借米谷为主、辅以富家捐助的兴建社仓的建议。所谓“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同共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日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与拨还。”[271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南宋时期有限的关于社仓的记载,证实当时社仓开设之初的米谷来源,是以向官府支借为主、民间捐助为辅作为基本形式的。如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中说到的大阐社仓最初的米谷来源是官府。由于原仓地址设置不合理,更改位置使得散敛更为方便。
招贤里大阐罗汉院之社仓,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为,而长滩之别贮也。始,秘阁魏君之筑仓于长滩……仓之所在,极里之东北,而距西南之境远或若干里,贷者多不便之。而是时率常数岁乃一往来,则犹未甚以为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发敛之政,而以岁贷收息之令从事。既为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时颁焉……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说告者……周君于是白于宋公,而更为此仓,以适远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输焉。来岁遂以远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岁得饱食,而又无独远甚劳之患,于是咸德周君。8]
福建浦城县的永利社仓也是如此。朱熹在《浦城县永利仓记》中说:
浦城县迁阳镇永利仓者,故提举常平公事黄侯某之所为也。闻之故老,某年中黄侯以乡人奉使本道,奏立是仓其里中,岁时敛散,以赈贫乏,且使镇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颇赖其利。后以兵乱废熄无余,岁或不收,民辄告病,于今若干余年……今知县括苍鲍君恭叔之来,乃复有请,而使者吴兴李侯沐深然之,于是鲍君得致其役。营度故壤,筑仓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旧制。。遂移县庾之粟若干斛以贮焉,夏发以贷,冬敛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仓制饬从事。[29]
福建邵武军光泽县社仓也是由官府支给,不过不是直接从常平仓中拨给米谷,而是从县财政的盈余之中,用籴米充实社仓,以及购置田产、籍没僧田等,以每岁所入米谷充实社仓。朱熹在《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云:
光泽县社仓者,县大夫毗陵张侯诉之所为也。适会连帅赵公亦下崇安、建阳社仓之法于属县,于是张侯乃与李君议,略放其意,作为此仓。而节缩经营,得他用之余,则市米千二百斛以充之。夏则捐价而粜,以平市估;冬则增价而籴,以备来岁。又买民田若干亩,籍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岁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仓,以助民之举子者如帅司法。既又附仓列屋四楹,以待道涂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栖托食饮,而无暴露迫逐之苦。盖其创立规模,提挈纲领,皆张侯之功。而其条画精明,综理纤密者,则李君之力也。[30]
朱熹曾撰写《常州宜兴县社仓记》,其中所谈到的社仓也都是由官府设置给谷,并由邑之贤者主持管理事宜。其中,朱熹高度赞扬了常州宜兴县知县高商老设置社仓,把官府常平仓的作用充分发挥于民间救荒之中。
绍熙五年春,常州宜兴大夫高君商老实始为之于其县善拳、开宝诸乡,凡为仓者十一,合之为米二千五百有余斛。择邑人之贤者承议郎赵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余人,以典司之。……会是岁浙西水旱,常州民饥尤剧,流殍满道。顾宜兴独得下熟,而贷之所及者尤有赖焉。……明年春,高君将受代以去,乃复与赵、周诸君皆以书来趣予文,且言去岁之冬,民负米以输者繈属争先,视贷籍无龠合之不入。予于是益喜高君之惠,将得以久于其民,又喜其民之信爱其上,而不忍欺也。31]
在朱熹所撰写的社仓记中,也有两篇记载社仓所存米谷是由民间士绅富户捐助的。《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云:
淳熙二年,东莱吕伯恭父自婺州来访余于屏山之下,观于社仓发敛之政,喟然叹曰:“……吾将归而属诸乡人士友,相与纠合而经营之。使闾里有赈恤之储,而公家无龠合之费,不又愈乎!”是时伯恭父之门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时已务赈恤,乐施予,岁捐金帛,不胜计矣,而独不及闻于此也,于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谷五百斛者,为之于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敛散以时,规画详备,一都人赖之,而其积之厚而施之广,盖未已也。[321
《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云:
是时南城贡士包扬方客里中,适得尚书所下报可之符以归,而其学徒同县吴伸与其弟伦见之,独有感焉。经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绍熙甲寅之岁,发其私谷四千斛者以应诏意,而大为屋以储之。……其为条约,盖因崇安之旧而加详密焉,即以其年散敛如法。乡之隐民,有所仰食,无复死徙变乱之虞。[33]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断言,南宋时期设置社仓之初的米谷基本上是以官府支借常平仓、义仓米以及利用财政盈余的款项籴米或购置田产等官出为主,而以民间捐助为辅。根据王文书研究,“从(笔者注:梁庚尧)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出,官方出资社仓占总数的52.3%,私人出资社仓占总数的23.1%,众人集资占总数的12.3%,官、众合资社仓占总数的6.2%,出资情况不详的占总数的6.2%。官方出资和官、众合资相加占到58.5%。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仓都经营借贷,但是从这一不完全抽样调查中可以找出这样一个规律:官方直接出资的社仓占有很大的比例。”[34]这里所说的官方出资,基本是沿袭朱熹的支借常平仓米,以及支借地方财政的赢余部分。至于户部提出的义仓存谷加收赋税的做法,地方官员普遍担心遭受加赋的谴责,目前很少看到这种做法的记录。况且,由于其致使当时的社仓未能得到行政制度上的普及,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仓设置之初支借米谷的主要来源。
到了明清时期,则有不同。社仓所存米谷,基本上是以民间捐助为主。《明史·食货志》记云:
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折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阵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35]
明代是施行社仓比较薄弱的朝代,但即使是从有限的试行过程的记述中,我们还是知道当时社仓的存谷全部来自民间,“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对于社仓之设都比较重视,加上这三朝的社会经济总体状况良好,所以朝廷推行社仓制度比较容易得到施行。但是从社仓设置之初的存谷情景看,也是以民间捐助为主要途径。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上谕云:
谕于各村庄设立社仓,以备饥荒。如直隶设立社仓,果有益于民生,各省亦照此例。嗣廷臣等议定,社仓之谷,于本乡捐出,即贮本乡,令诚实之人经管。上岁加谨收贮,中岁粜借易新,下岁量口发赈。[36]
康熙五十四年(1715)议定直省社仓劝谕之例:
凡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多捐一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绅衿能捐谷四十石,令州县给匾,捐六十石,知府给匾,捐八十石,本道给匾,捐二百石,督抚给匾。其富民好义,比绅衿多捐二十石者,亦照绅衿例,次第给匾。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部给以顶带荣身。凡给匾民家,永免差役。[37]
康熙年间社仓存谷由民间捐助的办法一直延续到雍正年间,但是在少数地方也出现了犹如南宋义仓加税派征的情况。对此,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1724)特地下道谕旨,强调社仓由民间捐助而不得于正税之外滥派的宗旨:
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则莫便于社仓。前谕尔等,劝导建设,盖专为安民起见也。尔等自应转谕属员,体访各邑士民中,有急公尚义之心者,使主其事。果掌管得人,出纳无弊,行之日久,谷数自增。至于劝捐之时,须俟年岁丰熟。输将之数,宜随民力多寡。利息从轻,取偿从缓。如值连年歉收,即予展限,令至丰岁完纳。一切条约,有司毋得干预。至行有成效,积谷渐多,该督抚亦只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使社仓顿成官仓,贻后日官民之患。朕初意如此,孰料该督抚欲速不达,令各州县应输正税一两者,加纳社仓谷一石。且以储谷之多少,定牧令之殿最。最近闻楚省谷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是为裕国乎?抑为安民乎?谕到该督抚速会同司道府等官确商妥议,务得安民经久之法以副朕意。
嗣复奉谕旨:社仓之设,原以备荒歉不时之需,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烦扰。朕以为奉行之道,宜缓不宜急,宜劝喻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是在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益,而无社仓之害。尔督抚当加意体察。至是议定社仓之法,一令地方官开诚劝谕,不得苛派米石。[38]
由上可知,清代的康熙、雍正年间,朝廷对于社仓的政策,都是以民间捐助米谷并由民间自主管理为主的。虽然也有少数地方官员试图通过正赋之外加派的方式筹集社仓的存量,但是被雍正皇帝发现之后予以禁止。除此之外,雍正年间也有少量像朱熹当年设置社仓那样,由官府的常平仓内支借部分米谷作为民间社仓本谷的,如云南省于雍正十三年定云南社仓之法:
云南设立社仓,通计一省所捐谷麦七万余石,其中十(千?)石以上者仅二十余处,此外皆数百石、数十石,亦有全无社谷者。至是议准云南各属皆有常平仓及官庄等谷存贮尚多,可酌量暂拨以作社本,将社仓存贮未及千石者,按地方之大小计存贮之多寡,于该处常平、官庄等谷内拨动五百石或八百石,作为社本,令社长一并经营出借穷民。秋成加一还仓,小歉免其取息,归于社仓项下积贮,俟积有千石,仍将原动常平等谷归还原款。[39
再如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求借用陕省火耗银8万两采买社仓谷麦,奉旨与甘肃巡抚石文焯商酌为之。[40陕西地方志也记载:“社仓,陕省向无社谷,雍正七年督院岳钟琪奏准,将应免五分耗羡银积存买粮,以作社本。”[41]不过就康熙、雍正年间的整体情景而言,这种官借社本的形式在清代前期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形式而已。
乾隆朝是清代最鼎盛的时期,乾隆皇帝对推行社仓制度特别用心,特别是强调在行政制度上予以保障和施行。在他的推动下,乾隆年间成为清代施行社仓最为繁盛的时期42j,也是宋代以来施行社仓最为繁盛的时期。为了使社仓的设置、管理以及敛散制度更为完善,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直省督抚地方官,开展对于朱熹《社仓事目》的大讨论。是年年底,御史朱续晫请将朱熹《社仓事目》发交各省督抚悉心讲究。十二月初一日上谕要求:“著各省督抚悉心详议具奏。”乾隆五年正月,户部咨文发给各省督抚。[43]于是在这一年,各省督抚纷纷把讲究的意见上折奏覆朝廷。这里,兹举闽浙总督德沛于七月初一日的奏覆为例。德沛按照朱熹《社仓事目》中的主要十一条目逐次检讨福建社仓的实施情况(在此略去朱熹《社仓事目》中的原条款)云:
一,《事目》内开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保簿重行编排……等因。查此条与保甲之法实相为表里,今保甲屡经严饬地方官实力遵行,其甲排甲册即事目所载保簿也。现行保甲烟户之下,原令开填户丁数目并作何生理字样,凡借贷给赈查照甲牌大小口核给,责成保甲长开报缴县察对,无伪给发,社长、社副依状支散,其逃军无行之人以及增添漏落之处,均难弊混。至所云乡官即今之社长、社副,名异实同,似可毋庸再设乡官,及编甲排甲册,应照现在条规遵行。
一,《事目》内开逐年新陈未接之际,预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给贷……等因。查委员监贷,原恐乡官蒙混而设,如果查系立品端方、乡间推重之人,充为社长、社副,又经立有劝惩之条,有过即惩,有善即奖,是劝惩明而商罚昭,则支贷自必公平,如再另委员役未免繁扰。况小县仅设一知一典,更难分身遍为监贷。此即朱子原札所云风土不同、随宜立约、申官遵守也。
一,《事目》内开申府差官讫,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等因……臣思欲收实效于日后,莫若立法于事先,应请先于造册时,细加区别,于人户之下注明士、农、工、商、不事生业五项,又于士、农、工、商之下注明需贷、不需贷,于不务生业下注明不、准贷各字样,支贷时即以此册为据,则扶同冒领之事无待临时稽查,互保自无弊混。
一,《事目》内开支收米用官斗,仰斗子依公平量。等因。查社谷出入原令均用官斗,兹应再饬令社长、社副各置升斗一副,送县较准,印烙发用,俾出入自可均平。
一,事目内开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官米,即开两仓,存留一仓,……等因。……应请酌量年岁之丰歉,计算人口之多寡,随时呈报上司,斟酌举行,庶事无拘泥而缓急有济。
一,《事目》内开入户所贷官米,至冬纳完……等因……至闽省息谷现准部咨,议准前署抚臣王士任条奏丰岁收息一斗,歉岁免息,已经通饬遵照在案,于仓谷、民生两便,其免二斗加三升之处毋庸再议。
一,《事目》内开申府差官讫,即一面出榜排定曰分,分都交纳……等因。……应令该州县于收放时剀切再行示禁,则自无守候、需索之弊。
一,《事目》内开收支米讫,逐日转上本县所给印簿,事毕具总数申府县照会……等因。……今再设印簿稽考,更为周备,亦当一体遵行,以重积储。
一,《事目》内开排保式甲户内开明大人若干口、小儿若干口……等因。查此条应即于保甲册内逐一编明,事属简便,可无弊混,似毋庸重复编造,以免纷扰。
一,《事目》内开队长阙社首依公差补,社首阙即申尉司定差。等因。查昔有队长、社首等项名目,今设社长、社副,酌古而不泥于古,虽今昔异名,其实总署一致,如有阙额,公择端方有品之人即行充补,以专责成。
一,《事目》内开簿书锁钥乡官公共分掌。等因。查收散社谷,州县设有印簿二本,一付社长收执,一缴州县存查,出入既有所稽,不经胥吏之手,自无滋扰之弊。互相稽查,深属得宜。再,查康熙十九年钦奉圣祖仁皇帝谕旨,义仓、社仓永免协济外郡,实为劝谕备赈之至要,自应敬谨遵守奉行。如地方官有抑勒、那借等弊,许社长、副以及捐输人户赴上司衙门呈控参处。庶官吏知儆,积贮充盈,俾严疆要地实有备而无虞矣。[44]
乾隆四年至五年,朝廷与地方督抚所进行的关于朱熹《社仓事目》的讨论,一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社仓设计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实推进了乾隆时期社仓的发展。综合各省督抚的讨论奏折来看,乾隆时期的社仓在各省已经普遍设立,社仓的设置与管理制度也较为完备。各省督抚在遵循朱熹《社仓事目》条款的同时,也会因地制宜适当调整某些措施,使得社仓的运行更为适合清代的实际情况。[45]
在乾隆皇帝的大力倡导之下,当时的社仓有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在乾隆前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财政的许可,各省督抚及地方官员也都努力在各地规划推动社仓的建设与施行。社仓几乎遍布全国各个行省,官府向民间社仓,尤其是一些边远地区和穷困地区社仓支借官本的现象有所增加,社仓的存谷数量也都较以往有所增加,有些地方的增加数量甚至相当可观。但是从整体上看,清代的康雍乾时期,民间捐助依然是社仓之谷的主要渠道。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宋邦绥在谈到该省的社仓存谷时说:“前任抚臣李绂题明动拨常平谷石借民收息,立为社仓谷本,嗣后酌定大、中、小州县分贮,自四千石以至三千石不等,名为社谷,实与常平无异,非如他省民自捐输者可比。”乾隆三十二年,江西巡抚吴绍诗也在奏折中说:“江西社谷向系捐自民间,现在每州县本息社谷,查据各属册报,自二三万石至六七千石,最少亦二三千石不等,通省共计七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余石,不为不多。”[46]从这些奏折中,我们不难看到乾隆年间社仓存谷来源的大致趋势。当然,清代是所谓“捐输”名目最多的时代,各种花样的“捐输”带有强迫性的意味很明显。清代社仓存谷的以民间捐助为主,其中带有强迫性的因素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在一些比较偏远以及穷困的地区,政府借本、出本设立社仓的现象也有所增加。无论是民间捐助,还是政府借本、出本,清代乾隆年间社仓的兴盛,都与政府在行政上的大力推行有着直接的关系。
乾隆年间的社仓设置与运作虽然达到宋代以来的最高峰,但是由于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一部分地方督抚及地方官员,往往投其所好,夸大地方设置社仓的实际效果,虚报社仓的数量以及社仓存谷的数量。致使在清查的过程中,时有发现社仓存谷与实际盘点数额不符的现象。如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朝廷派官员核查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嘉兴等地的社仓,就发现其中缺额者甚多,管理不善,“据窦光鼐奏,盘查过嘉兴、桐乡、海盐等六县仓谷,有缺谷数数百石及百余石者……桐乡县仓内实无储谷,所有之谷乃借自折仓;又借米三千石开报平粜,掩饰一时。嘉兴县折仓空虚,呈控纷纷,是该二县社仓办理皆不妥协。”[47]乾隆三十五年,清查苏州等富庶地区的社仓存谷,也发现册上之额与实际存粮数额的较大差距,“经查核,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属各社仓,应储之额虽有二十六万九千余石,严饬核实清厘,内中存价未买者有六万数千石,社长侵亏者六百余石,历年出借在民者一十六万三千余石,稽其实存在仓仅四万余石……责成巡道严行督催稽查,务必令悉归实储。”[48这些流弊越到乾隆晚年及其后越发严重。
再者,乾隆年间社仓的发展得益于乾隆皇帝及朝廷的强力推行,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就存在政府过多干预社仓日常运作的情景。康熙、雍正年间,社仓的运行情况一般不必题报政府,如上举雍正二年的谕令,“该督抚亦只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但是在乾隆年间,社仓数额及存谷数额不仅要题报朝廷,而且在散敛等诸多环节,都得经过官府的允许,“社仓既有报部之议,则经理须归有司之手”。[49]当地方官府在其他财政支出上出现困难时,就难免挪用社仓米谷来应急。如乾隆二十六年安徽省就想把社仓息谷挪用来修筑常平仓库,“安徽省现需修建仓廒,无款可动,请酌拨社仓息谷,变价以济工需。”[50]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江西巡抚郝硕奏请循福建等省成例酌变社仓息谷以充地方公用,他依据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间安徽、福建二省奏请,将社仓息谷变价解司,以充地方公用。“按其所存息谷数目,照依时价出粜,将价解司贮库。遇有农田、水利等务为民间必需工作势不可缓者,奏明动用,报部核销”,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山西也是如此,乾隆四十年布政使黄检为变通社仓义仓息谷变价解贮司库事上奏,“其余息谷三十五万八千七百余石,请令各州县于粮价稍昂之时详请价值,酌量售粜,事竣即将谷价解贮司库……并于要事公费均有预备动用之款。”[51]这样的变通是朱熹当年设计社仓时所万万未能想到的事情,已经超出了社仓备荒、救荒的初衷。
通过以上朱熹社仓设计及其流变的分析,不难看出:朱熹当年设计并亲自实践的五夫社仓,起到了备荒、救荒的社会功能,宋孝宗批准社仓建议推行于天下时,由于执政部门(即户部等)规定了社仓设置之初的官本必须在正税之外附加征收,大多数地方官员虚与应付,碍难施行,致使朱熹的社仓设计并没有得到行政上较为广泛的普及,而只有一些道德上的模仿。尽管如此,朱熹的社仓设计对于后世却影响深远,特别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当政者每每以朱熹的《社仓事目》为指南,大力推行社仓制度,在行政制度上予以相应的保障与施行,以至清代乾隆年间成为朱熹之后践行其社仓理念最繁盛的时期。换言之,南宋时期朱熹所设计的社仓制度是在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得到行政上的真正施行。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社仓制度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与朱熹原先设计条款所不甚一致之处。我们通过从南宋时期以至清代社仓的变迁历程,更可体会到朱熹所具有的长远文化精神。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又载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朱汉民
什么是义理之学?历史上,人们把那些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称为“义理之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代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人们的思想或者印象中,义理之学似乎就是一种对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义的体悟。义理之学成为脱离实际、空疏无用的知识学问。这和历史上义理之学的本义以及后来的思想发展完全相脱离。本文试图对宋儒的义理之学重新诠释,以求获得对义理之学的合理理解。
一、“义理”的本义
当清代学者将宋学定义为“义理之学”时,是为了与他们心目中的“汉学”区别开来。他们主要是以知识学意义上的学术范式差异来理解“义理之学”的“宋学”,即将“宋学”视为一种以道德义理的诠释、思辨为重点的义理之学,以区别于以文字、文献和典章制度为重点的考据之学。但是这与宋儒自己所理解的“义理之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宋儒称自己的学说为“义理之学”“理学”时,其意义首先是学术的社会使命与文化功能意义上的,即他们旨在恢复原始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旨在恢复与建构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圣学”以解决社会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问题。其次,“义理之学”“理学”当然也是学术范式、知识形态意义上的,“义理之学”的目的是要恢复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圣学”的文化功能,故其学术范式必须采取道德义理的诠释、思辨为重点的义理之学的学术形态。
从社会功能、学术范式的双重意义上考察宋儒“义理之学”,我们必须首先厘清:这个在文献典籍上耳熟能详的“义理之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所以必须进一步探讨“义理之学”中“义理”的历史含义。
“义理之学”是宋代出现的,而“义理”或者“理义”则是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同时在双字词“义理”“理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理”“义”的单字词,并且有了确切的哲学含义;至于单字“理”“义”组合而成的“义理”“理义”,则是其哲学含义的深化。
在先秦文献中,“义”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其词义也较丰富,但是,其主要意思则是正义、道义、德义相关的道德概念,涉及的是与人的道德价值相关的精神世界。人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诸多道德准则、道德范畴的一种,如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诸多德行、规范的根本准则。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说“义,群善之蕝也。”(《郭店楚墓竹简》,第179页)
在先秦文献中,“理”也是一个大量出现的词,与“义”主要是一种道德意义的价值概念不同,“理”最初就是一种法则意义的客观规律概念。据学者邓国光考订“理”最早见于典籍是动词“整理”“治理”的意思,“与治国的‘疆理天下’的重大事件相关”(邓国光,第6页)。由动词的“理”转化出名词的“理”,就具有了客观法则的意义。对于古人来说,客观法则的“理”可以是自然法则,即所谓“物成生理”(《庄子·天地》),“万物殊理”(《庄子·则阳》),“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韩非子·解老》);也可以是社会法则的理,即所谓“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墨子·非儒》)“故礼者,谓有理也。”(《管子·心术》)
在先秦文献中,当独立的“义”字、“理”字出现以后,又产生了将“义”和“理”连用的“义理”或“理义”。这种连用的“义理”的结合一般形成三种词组结构,并形成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理”与“义”并列义,如《墨子·非儒》有“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就是一种“义”与“理”的并列。所以《管子·形势解》说:“国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同时又指出:“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这里分别出现“理义”和“义理”,说明其“理”(法则)与“义”(道义)的并列关系。其二,是以“理”定义“义”的偏正结构。如孟子向来重视道义,多讲“义”,但偶尔也说“理义”,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孟子所说的“理义”,旨在强调“义”的内在必然性,故以“理”修饰“义”。其三,是以“义”修饰“理”的偏正结构。《管子·心术》说:“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管子重“理”,故而他说的“理”是社会法则,他特别强调“理”的法则必然决定“义”的道义应然。
在先秦诸子中,大多都要讲“义”“理”或者“义理”。但是,先秦儒家重道义故而主要讲“义”;而先秦道家、法家重自然法则或社会法则,故而主要讲“理”。一般而言,那些重视人文理想的学者、学派偏重道义(义)的重要性,而重视现实功利的学者、学派则偏重法则(理)的重要性。
对于以典籍知识为职业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写书的目标就是探求和表达“义理”,即确立道义与法则。至于古人留下来的经典,其根本要旨就是承载、传播“义理”。所以,在“义”“理”观念形成的同时,如何从经典中寻求义理就是其读书人的首要目标。《周易》是群经之首,先秦儒者就是希望探求圣人表达的“义理”,故而《周易·说卦传》提出圣人作《易》时,“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颖达《疏》云:“以治理断人伦之正义。”这确是体现出儒家的义理观,即以“正义”的道德价值去“治理”现实的政治秩序。所以,两汉时期确立了儒家经典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后,如何从经典文献中探寻义理就成为儒家经学的使命。这时,与经学相关的概念大量出现,诸如: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王充,第256页)
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王充,第556页)
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唐六典》,第45页)
汉唐时期的儒家经师、学者,以研究经典的文辞章句为业,但他们也意识到,通过经学的训诂章句的研习,旨在“辨明义理”,即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
正由于儒家的“义理”包含着“义”的道义与“理”的法则,所以,尽管“义理之学”的兴起本身是一种学术范式的重要转折,即由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转换成两宋的义理之学,但这种学术范式的发生转换的内在动力、思想根源是复兴儒学的文化功能、政治使命。这种文化功能、社会使命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阐发儒学的道义价值内涵,激励儒家士大夫追求“道”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则是要推动儒学治理社会的实用功能,能够指导儒家士大夫在治国平天下活动中建功立业。
二、宋儒义理之学的双重含义
“宋学”所具有的“义理之学”形态,绝不是被许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空谈义理的学说,相反,它从产生就是旨在创建一种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学说。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
从历史事实来看,那种将宋学等同于宋代理学的传统看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两宋时期的学术思潮中,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学术主旨的观点与流派,以“道学”“理学”自命的伊洛之学只是诸多学派中的一派,其他还有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等。不仅是这些诸多的学者、学派均活跃于宋代学术思想界,而且他们的学术旨趣、思想观念具有“宋学”的“义理之学”共同特点,就是所谓明体与达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统一的特点。
首先,宋学学者均希望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义理探求,建构一种道德性命之理,以解决世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问题。其实,宋学学者的不同派别均重视义理之学,他们之所以强调经典的义理重于训诂章句,就在于义理能够解决人心世道的价值建设问题。在宋学的义理之学中,“义”的儒家道义价值重振,一直是宋学学者所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推动宋学初兴的范仲淹,即是一位执着于复兴儒家道义价值的士大夫,他们“慎选举,敦教育”,主张“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范仲淹全集》,第237页)。他倡导“举通经有道之士”,在科举中将经义置于章句之上,均是为了整顿士风、重振儒家道义。被称为宋学奠基人的“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均是在宋初主张重振儒家道义的著名学者。胡瑗主张学术、教育应该坚持“有体、有用、有文”,其具体就是“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的儒家伦理、道义的价值信仰;孙复研究《春秋》学以求本义、大义,此“义”也就是仁义礼乐的道义价值,他希望在宋初能够重振儒家道义。石介倡道统论,这个“道”即是儒家推崇的道义价值,所谓“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徂徕石先生文集》,第245页)另外,王安石所创立的荆公新学,同样一直是以复兴“先王之道德”为己任,以重振儒家道义价值作为其学术的根本。他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临川先生文集》,第859页)他主张儒家道义价值的“性命之理”是人心本有的,从而为复兴“先王之道德”确立形而上的前提。与荆公新学同时崛起的洛学、关学等“道学”学派,更是以重振儒家道义价值为己任。他们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相通的义理之学,其目的就是重振儒家伦理,推动仁义礼智信的道义价值建构。如朱熹特别推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书,就在于四书包括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他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朱子全集》,第3640页)由此可见,在宋学学者群体中间,无论是哪一派学者,他们希望复兴三代先圣、先秦儒家道德思想、价值信仰似乎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宋学学者均有很强的经世致用追求,无论是通过经典诠释而建构义理之学,还是直接从历史、现实中探讨经世之学、治世之方,宋学均十分关注并希望最终解决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问题,包括革新政令、抗击外辱、民生日用的治国平天下问题。宋学作为一种纠正汉唐以来“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的学术思潮,他们与那种纯知识化的章句之学有完全不同的学术旨趣,就是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前面所述的那些复兴儒家学说、推崇道义价值的宋学学者,恰恰也是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追求、致力于革新政令事务的士君子。宋学的开拓者范仲淹就是北宋“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他的经义创发、师道推崇、士风重振的道义关怀,其实均是与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选拔人才的经世致用目的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所表达的正是宋学革新政令的经世追求。宋学开创之初的“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创发经义的道义关怀,也是与革新政令的经世追求是一体的。胡瑗强调“明体达用”,其“用”就是“举而措之天下”的经世追求,他在湖州时创“经义”“治事”二斋分科的教学,其“治事”斋要求“治民以安其身,讲武以备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黄宗羲全集》,第56页)孙复的《春秋》大义其实就是基于现实的经世追求,即如欧阳修所说,是“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欧阳修全集》,第458页)在北宋时期,创发经义、革新政令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无疑是王安石。王安石的“经术”与“经世”是统一的,他对神宗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宋史》,第10544页),并由此推动的熙宁变法,来实现他创通经义的目的。应该说熙宁新政是继庆历新政之后一场更加重大的革新政令的运动,充分体现了宋学所具有的强烈经世追求。同样,宋学中其他学派诸如:关学、洛学、闽学等,虽然他们对经义道德、心性修养、形而上思辨方面更加关注,并且更加标榜自己的学说是“内圣之学”“义理之学”,但是他们作为宋学的最重要力量,仍然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经世追求。张载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恰恰是道义情怀与经世追求的统一,他所希望的恰恰是长治久安、太平之世的“三代之治”。二程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只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同,但他们均主张以经术经世务,以治国平天下为学术最终目的。
所以说宋学所追求的“义理之学”,其“义理”的含义正好包括了道义关怀的“义”与治理天下的“理”。几乎所有宋学学者、宋学学派,其实均是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经义与治事、道与治、道义与事功、世道人心与经世致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的统一。当然在宋学内部,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与学者,他们除了对经义有不同理解、对政令有不同主张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事功关系上,更加偏重于某一个侧面。在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义理之学”中,究竟是“义”的道义决定“理”的政治治理,还是“理”的政治治理统摄“义”的思想道义?两宋时期最大学派之争,就有北宋王安石新学与二程洛学,还有南宋朱熹的考亭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之争。他们的分歧并不是“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而是道义价值、政治事功两者中谁最根本、更优先。二程、朱熹重道义价值、内圣修养,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道义价值、内圣修养的问题,然后即可实现经世治国、外王事功,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而王安石、陈亮则相反,他们特别强调经世治国、外王事功才是思想道义的前提与目的,道义价值、道德理想最终只能通过治国安邦、外王事功方能得以实现。朱熹和陈亮的学术争辩,就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层面。朱熹认为只有三代时期的内圣道德与外王事功才是统一的,秦汉以来尽管出现了汉高祖、唐太宗等杰出的英雄豪杰,能够治国安邦,创造事功,但是他们均无内圣道德。他说:“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都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朱子全书》,第1558页)三代君主皆是由内圣而外王、由道德而事功,故而才是合乎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三代之治。但是陈亮的看法恰恰不一样,他肯定汉祖、唐宗的治国安邦之政治事功的道义价值,他说汉祖、唐宗“终归于禁暴戡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领宏大开廓故也……此儒者之所谓见赤子入井之心也。”(《陈亮集》,第346页)朱熹等理学家坚持道义价值、内圣修养是义理之学的根本,三代王道理想的实现首先就在于诸位圣王坚守了道义的价值与内圣的修养,至于治国安邦、外王事功则只是内圣道德的自然结果。而陈亮则坚持以治国安邦、外王事功作为根本,认为“赤子入井之心”必须依托、呈现在这种治国安邦、外王事功之中。由此可见,尽管朱熹、陈亮均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有体有用之学,均属于义理之学为学术旨趣、学术形态的“宋学”,只是他们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功利方面的不同基点与侧重,从而构成宋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虽然程朱学派在当时及后世被称之为“理学”,其实他们所推崇的“理”主要是道义的价值,故而是“以义为理”;而荆公新学、浙东学派则强调治理国家的功利目标及现实法则,即所谓“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黄宗羲全集》,第56页)他们的义理之学应该是“以理为义”。
三、宋儒义理之学的学术领域
宋学的义理之学追求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故而宋学学者、学派显然不仅仅是宋代理学家、理学学派,而是包括宋代各儒家学者与学派,且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当然是十分多样化的。宋学学者的著作分布在经史子集的不同知识部类中,涉及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文学乃至农、林、医、艺等不同学科。所以,许多学术史叙述将宋学窄化为理气心性的抽象义理,其实不是宋学学者的学术视野狭窄,而是后来学人的学术偏见。在宋学的这些研究领域,均体现了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双重功能要求。
宋学首先体现为对儒家经学诠释的学术创新。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往往将宋学理解为宋代经学,这种理解,其实与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与核心有关。在古代中国,一切思想演变、学术发展、文化转型,均要体现为儒家经学的变革与创新。宋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和重要的学术形态,首先体现为一场经学的变革。正如清学者钱大昕所评述的:“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11页)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王安石、程颢程颐兄弟等均是宋学的开拓者,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各出新意解经”,这一“新意”也就是经学史上反复称谓的“义理之学”。他们特别重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但他们与汉唐诸儒究心于经典的章句训诂不同,而是特别重视对经典的义理探寻。上述的欧阳修、二苏、王安石、二程等宋学开拓者,其实均是以义理解经而获得突出成就者,他们的经学著作,如欧阳修专注“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为古人所未见。”(《欧阳修全集》,第2713页)故而是宋代义理之学的开拓者。王安石也是如此,南宋赵彦卫说:“王荆公《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赵彦卫,第135页)王安石《三经新义》包括对《周官》《尚书》《诗经》三部经典的义理之学。二程亦是以义理解经的大家,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宋学以义理解《周易》的代表作。
宋学不仅通过对传统的“五经”的创发,建立了新的学术范式的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新的经典体系的创建者,他们建立了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中心的新经典体系,并对这四部经典做了系统的诠释,使宋学的哲学观念、政治思想、修身工夫等理学思想与“四书”经典紧密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经过宋学学者的经典建构,中国传统经典体系就不仅有“五经”体系,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甚至地位更高的“四书”体系。
宋学作为一种为强化儒学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文化功能的新兴学术思潮,推动了宋代以义理之学为学术范式的知识建构,最终目的仍然离不开推崇道义价值、经世事功两个方面。首先,宋学强调经典奠定人的道义情怀、价值信仰的根本作用。宋代学人对汉唐经学的不满,首先就在于汉唐学人将经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知识性的章句训诂之学,经典在塑造个体道德心灵、建构社会伦常秩序、奠定价值信仰上的根本宗旨被忽略了。所以,宋学的开拓者将学术重心放在重新诠释经典上,就是希望发挥经学在塑造个体道德心灵、维护社会伦常秩序、重建道德价值信仰上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经典中所阐发的义理,首先就是这种道德及其性命之理,王安石认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王安石全集》,第858页)王安石的“性命之理”的内容和二程所讲是一样的。程颐在阐发《周易》的义理之学就是社会道义价值,他在为《艮卦·象传》作传时说:“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二程集》,第968页)所以,宋学从经典中阐发的“义理之学”,特别强调社会伦理的道义价值。其次,宋学还对经学的经世功能特别追求,他们希望从经典中建构起一种能够对经世治国有实际作用的义理之学,所以,所有宋学学派、学者无不是将经学视为经世致用之学。那些以改革政令、经世治国为主导的范仲淹、王安石、陈亮、叶适通过经典的义理诠释,为现实的政治改革、经世致用服务。同样,那些强调身心修养、道德义理的理学家们,也是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义理经学的目标。如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均为二程理学传人,但是,他们研究经学、建构宋学义理之学的目标就是经世致用。胡安国终生从事《春秋》学研究,著有理学家治《春秋》的代表著作《春秋传》,他主张“《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宋史》,第12913页)而胡宏也强调“学”与“治”是一体的,他说“学者,所以学为治也。讲之熟,则义理明;义理明,则心志定;心志定,则当其职,而行其事无不中节,可以济人利物矣。”(《胡宏集》,第128页)正由于所有宋学学者均强调明体与达用、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故而宋代的经学就是一种将道义价值与功利价值、人格修养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的义理之学。
宋学不仅是指宋代的经学,同时还包括宋代的史学。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陈寅恪集》,第272页),宋代史学的发达繁荣,同样与宋学学者追求的道义价值、经世目的有密切关系。义理之学的价值理想是宋学推动经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同样是他们推动宋代史学繁荣的精神动力。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宋学学者们,往往既是经学家又是史学家;即使有很多学者完全是历史学者,但他们的史学观念仍属于宋学,其从事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仍是宋儒义理之学的价值理想与政治功能。宋代学者热衷史学研究、著有大量史学名著,其动力之一就是探讨历史治乱盛衰的规律,为当代政治人物提供治理社会国家的原则、方法、策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然而从这部著作的书名上看,这部史学著作的目的是供当代朝廷“资治”之用。司马光将历史看作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而其目的则是总结历史治乱兴衰及生民休戚的经验,满足当朝人物的执政需要。他最终编撰成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提供当代朝廷资治的著作。所以,该书很快就得到当朝皇帝神宗的肯定与赞誉,他认为这部书的重大价值就是:“其所以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司马光,第29页)司马光这种希望通过史学而探寻治乱之原、提供治国之鉴的想法,在宋代历史学家那里是十分普遍的。那些以理学为主导的学者也是这样,与司马光同时代宋学大家程颐就将史学看作是探讨治乱、安危、兴衰、存亡的学问,他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二程集》,第232页)程颐以义理经学见长,而他的史学观与司马光等历史学家相同,即希望从史学著作中满足当朝执政的需求。另外,那些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宋学学者,亦普遍是这种史学观。如南宋婺学学派吕祖谦以历史文献研究见长,他的史学观同样如此,他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吕祖谦全集》,第218页)可见,吕祖谦以历史文献研究见长,其动机目标也是希望通过史学来探讨治乱之原,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
宋代史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伦理的道义价值的重视。宋代史学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规律时,特别强调儒家伦理之道能够影响、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这样,宋学学者在史学领域特别关注价值与政治的结合。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本来就是德治、仁政,将天下国家的治乱兴衰归之于道义人心。所以,宋儒的史学著作特别强调道义人心对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希望通过写史以对朝廷、百官起到一种劝诫的作用。如北宋唐史名家孙甫的史学观就是如此,他以《尚书》《春秋》为史,认为“《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间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孙甫,第620页)以历史人物的道德善恶来说明政治治乱兴衰,以强调道义的正面价值和历史影响,最后达到对当朝君臣、士大夫的劝诫,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宋儒那明显得到进一步强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特点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第9607页)他明确将历史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与当朝君臣的善恶戒劝结合起来。吕祖谦的婺学偏重史学,与考亭学派以性理见长不同,但其史学仍然将“择善”“儆戒”置之首位。他说“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吕祖谦全集》,第257页)
宋学的学术领域除了经学史学之外,文学亦是一个重要领域。中国传统的“文学”比现在仅仅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的外延更大,它是指以文字、文章及典籍为载体而表达作者的观念、思想、情感的学科,既包括塑造形象,表达情感的艺术类文学,也包括通过思想陈述、逻辑推理以表达思想观念的论说类文章。宋学的兴起,与文学领域的一场重要转型或革命的发生是同步的,即唐宋之间发生的古文运动。宋学的形成和发展是承唐中叶以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发展而来,同样,宋代的古文运动亦是承接唐中叶以来的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而来。韩愈、柳宗元为抵御唐初文学的“六朝淫风”,力倡“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昌黎全集》,第219页)、“文者以明道”(《柳河东全集》,第542页),以复兴儒家之道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北宋时期推动宋代义理之学的领袖人物,恰恰均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可见复兴原始儒学的宋学思潮,是推动古文运动的根本力量。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文坛出现“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的局面。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如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孙复、石介、欧阳修、苏轼等重倡“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古文运动,以复兴儒家之道。其实,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追求,与宋儒所追求的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义理之学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主张,以新文体取代旧文体,其新文体包含的“道”恰恰体现为道义关怀与经世追求、内资修德与外济经世的统一,正是宋学所追求的学术精神。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子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欧阳修全集》,第978页)无论是学者学术追求的“道”,还是文章所要表达的道,均是必须能够“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明体达用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其实,这一观念,恰恰是宋代的学者文人的共识。譬如胡瑗主张为文、为学均得“以体用为本”,他坚持“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全集》,第25页)他认为一切文所载之“道”就是这种“仁义礼乐”的道义信仰与“措之天下”的经世之具。石介推崇的“文”也是如此:“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徂徕石先生文集》,第135页)“教化仁义”是明体之事、内圣之德,“礼乐刑政”是达用之功、外王之业,但均要通过文辞而表达、传播。又如李觏也认为,“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李觏集》,第288页)他推崇的这种“文”,也是包含着全体大用、内圣外王之道。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论宋代理学与新学的关系
——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
⊙蔡方鹿 李琛
宋代理学代表人物二程朱熹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宇宙观,以性善论为主的人性论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及与之相关的存理去欲的理欲观。理学由重义轻利和提倡道德自律而表现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则提出以元气为道之体的道本论宇宙观[1],“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2]的人性论,趋舍唯利害,“义固所为利”[3]的义利观。新学由重视事功和社会治理而表现出重外王的倾向。
理学与新学在宇宙观、人性论、义利观以及治国理政观念上的差异引起了双方的相互批评。但二者又同属重义理的宋学,又相互影响和沟通。理学的完善与确立,直接受益于新学。新学和理学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大发展。双方地位的消长,直接影响了后世学术与政治的发展进程。虽然新学在南宋时逐步失去了其在北宋时形成的官学地位,后又渐趋沉寂,但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本文就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异同互动关系,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理学与新学的相近处
理学与新学在宇宙观、人性论、义利观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治国理政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由此展现出两派思想各自的特点。理学重义轻利,主张节制统治者和人们的欲望以维护社会稳定,并通过存理去欲以恢复先天的善性,所以讲性善论。而王安石新学则在价值观上重视功利,发展了儒学中的“外王”部分,并将其义利观付诸实践,以义理财,推动新法改革的实施。因此,新学的义利观既是改革的理论需要,也是新法的理论基础。王安石强调:“世无常势,趋舍唯利害。”[4]他认为人们的进退、行为举止以趋利避害为原则,表现出对客观利害的重视。并认为取利、有用是天道自然的原则:“盖有常以为利,无常以为用者,天之道也。”[5]强调利是有常,用是无常,均为天之道,肯定利的用处和价值乃普遍的规律。在人性论上重视情,认为“性生乎情”,有了情才有善恶,不认同性善论。由此形成理学与新学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主要是价值观和人性论上的分歧。
以往学界对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差异论述较为充分,而对理学与新学存在着的相近之处则关注不够。以下着重探讨二者在同属宋学而批评汉学,既重视功利又重视道义,以及在尊王黜霸等方面的沟通与相近之处。
(一)同属于宋学而批评汉学
理学与新学都属于宋学,重视阐发义理,批评汉学单纯重考证训诂的学风。二程站在宋学的立场,主张道理可不受解释文义的约束,指出:“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6]把阐发道理放在首位,即使文义解错也无碍。程颐由此批评了只重文字训诂而不及道的学风:“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7]把经典作为载道的工具,指出只对经典文字加以训诂而不求道,不过是无用之学。朱熹继承二程,对汉儒偏重训诂而忽视义理的学风提出批评:“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8]以上程朱对汉学的批评,反映出汉宋学之别在于重训诂还是重义理。
新学作为宋学的重要派别,亦对汉学学风提出批评,这是其与理学家的一致之处。王安石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9]强调治经学以致用为目的,“学者不习无用之言”,这体现了王安石新学与汉学的差异。
这里王安石和程颐均把章句训诂视为“无用”之学,这是二者的相同处,共同体现了宋学通经致用的学风。王安石指出:“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10]其对汉学的批评成为理学的同调。正如李存山先生所指出:“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批评科举考试,‘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新义》颁布于学官,至此,‘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李存山)认为王安石新学批评汉学崇尚章句文辞之病,并颁行《三经新义》,以宋学取代汉儒之学,是因为受到范仲淹的影响可溯源于庆历新政。新学的这一思想与当时理学家批评汉学的倾向是一致的,而同属于宋学。
(二)理学家亦有重视功利而与新学相近的一面
以往认为,理学家重义轻利,与新学重视功利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故在变法指导思想上出现对立,分为各自不同的派别。这种认识虽有道理,但还须进一步探究。新学对客观事功和利益的重视不言而喻,然而理学家也并非只讲义理不讲功利,亦具有与新学的相近处。
二程重视义利之辨。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11]]认为天下之事都可用义利标准加以衡量。他认为不得抹煞利的存在,而应肯定利的作用。程颐说:“‘故者以利为本’,故是本如此也,才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顺,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112在解释“故者以利为本”时,程颐充分肯定利原本就具有的价值,而不是排斥利。认为利的存在,与性密切相关,不利则会害性。如果人无利,便失去了人生存的条件。因此承认“天下只是一个利”。但对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利的进一步追求,程颐表示要加以控制,以防止“趋利之弊”。二程更多地强调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利,认为“水利之兴,屯田之制,府兵之复,义仓之设,皆济世之大利”[13。这体现了二程对功利的重视。
朱熹在重视道义的同时,亦重视功利,提倡义利统一而不空谈道义。他说:“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14所谓“义未尝不利”,便是义利统一,在讲道义之时,利也在其中。并强调讲道义是为了求利。“义有大利存焉”,义之中就有大利,义不能脱离利而存在。这表明义利共存,不可分离。并继承二程的义利观,指出:“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15]朱熹在引用二程“君子未尝不欲利”的观点时加以发挥,认为专门讲利则有害,而以仁义为指导,即使不去求利,也会带来客观的物质利益。可见理学家并不排斥功利,而且在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程颢、朱熹、张縂、吕祖谦等著名理学家关心民众疾苦,视民如伤,在各自的任内做出不少有利于民生的实事。这表明,理学对于功利并不是排斥的,而是把功利包含在道义和义理之内而加以重视。这与新学有相似之处。
(三)新学亦有重视道义而与理学相近的倾向
以往认为,新学重视功利,理学重视仁义,在变法指导思想上形成对立而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对峙,并影响了两宋时期思想学术与政治的演变。但新的研究表明,新学在重视功利的同时,亦有重视道义的倾向,这与理学相近。如王安石指出:“彼区区聚敛之臣,务以求利为功,而不知与之为取,上之人,亦当断以义,岂可以人人合其私说,然后行哉?”[16]王安石主张把功利与义结合起来,使功利符合义的原则,并不完全只重功利。他还指出:“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17王安石在重视功利、经营天下财富的同时,更重视道义的指导,强调理财不可无义。尽管需通过理财来满足天下人的财货需求,但王安石主张理天下之财不可脱离义的指导,表现出义利结合的倾向。
熙宁变法期间,当神宗询问制置条例的新法制定如何时,王安石向神宗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118]指出治国理政应有先后缓急,如果强调理财,就会重视“使能”,而将“任贤”置之于后,造成朝廷只务理财,而对礼义教化未有顾及,以至于带来风俗弊坏的消极后果。所以王安石认为还是应以礼义教化为治国之先。可见新学在实施变法时,也是主张任贤,重视教化的,而且对理财加以一定的规范,在理财的同时不放弃“礼义教化”之道义。
进而,王安石把理财本身就看作义。他说:“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19]指出政事是为了理财,理财乃为民的公义。王安石对利加以解释,把利界定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认为周公作《周礼》,重视理财,提倡为民之利。可见礼义、道义与利不可分。他还主张公私兼得:“故市不役贾,野不役农,而公私各得其所。”20]提出公私结合,而不是排除私人之利。并作诗以肯定“道义”:“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21]这表现出王安石重视道义,并一定程度地肯定孟子和韩愈的思想倾向。
(四)双方都重视尊王黜霸,批评霸道政治
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反对霸道,提倡王道;主张行仁政,以仁义治天下。王道即尧舜、三代先王之道。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22]霸道是指凭借武力假借仁义以征服别人。“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3]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认为春秋五霸行霸道,与王道相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24]即齐桓公、晋文公等是夏禹、商汤、周文武王的罪人。后来荀子主张王霸不偏废,“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25]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认为儒家王道已过时:“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6]强调与以力相争的时代相适应的只能是霸道,如果不行霸王之道,只会带来乱世。“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27]并指出,儒家的仁义不足以治国,尧舜之道也不能为治,称赞被孟子批评的齐桓公:“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8]表现出法家的霸道与孟子王道思想的对立。
秦汉以后王霸并用,霸王道杂之。至宋代,关于王霸之辩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
程颢指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炫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29]把王道加进了天理的内涵,体现出其时代性。程颢既批评假借仁义以行霸者之事,又批评以霸者之心来求王道。指出孔子后学之所以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曾耻于与管仲为伍,是因为“义所不由”,即推行霸道,违背了仁义的原则。表现出程颢在新形势下尊王黜霸的思想。朱熹继承孟子、二程,讲王霸之辩。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齐桓、晋文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设使侥幸于一时,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则固霸者之道也。故汉宣帝自言汉家杂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30]朱熹指出王者之道是致诚心以顺天理,使天下服。而霸者之道乃假仁义以济私欲,如春秋五霸之齐桓、晋文。在朱熹看来,王霸之辩在于是否顺天理或假仁义,即以义利、公私、理欲作为划分王霸的标准。
尽管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重视功利和外王,在变法中积极推行各项社会改革措施,但他对王道政治仍表示认同,并批评霸道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的尊王黜霸思想。他说: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何也?盖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其功异则其名不得不异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为也,唯恐民之不见,而天下之不闻也。故曰:其心异也。[31]
王安石论王霸之别,认为其用相同,表面上都讲仁义礼信,但其心则不同,王者之道认为仁义礼信是原本应当为的,所以以仁义礼信修其身,并移之于政治,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无不化。但霸者之道则不同,其心并不在仁,只是担心天下人恶其不仁,所以表面上也讲仁;其心也不在义,只是担心天下人恶其不义,于是表面上示之以义。对于礼信也是这样。所以说霸者之心是为了追求利,而假借王者之道以求其所欲。这表明在王安石看来,王者和霸者,其思想实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此而言,王安石区分王、霸的目的,是批评霸道政治,主张实行仁义礼信之王道政治。这与程朱等理学家批判的假借仁义而行霸道的王霸之辨有类似之处,亦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
二、新学对理学的影响
由五经训诂之学转向为四书义理之学,体现了由汉学向宋学的时代转型,这与王安石新学对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四书义理之学伴随着宋代《孟子》的由子入经而逐步形成。虽然二程在唐代韩愈、李翱开重视四书之先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孟子》等四书的地位,但二程的影响力有限。而王安石在当时则身居高位,领导变法,直接对科举进行改革,使四书这种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得到官方的认可,更把《孟子》《论语》规定为官学教材,为《孟子》的由子入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理学家难以相比的。
在上述方面,新学对也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王安石倡导义理和道德性命之说,批评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与理学的学术旨趣相近,而且王安石在主持当时的熙宁变法中直接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规定不用注疏,务通义理,更把《孟子》等定为兼经,完成了把《孟子》上升为经书的过程。中书言:“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32]在废除以诗赋取士的同时,规定以《论语》《孟子》为兼经,这为四书系统的形成和四书义理之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务通义理”的宋学逐渐替代了重视训诂考据的汉唐注疏之学,并为宋学之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马端临指出:“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则于学者不为无补。”[33]所谓“变声律为议论”,即指以己意说经的议论之学代替讲究语言声调韵律的诗赋之学;而“变墨义为大义”,即是以义理代替记诵,认为王安石这种对科考的改革,有补于学者。又颁行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于全国。“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34]汉唐传注之学废而不用,使得对整个儒家经典的诠释之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转折。王应麟对此加以评价:“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35]王安石新学的兴起以《三经新义》为文本,以讲义理为重,成为汉儒训诂之学被宋代义理之学所取代的重要表现。这对宋学之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理学与新学在同属宋学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新学亦遭到了程朱等理学人物的批评,但新学和理学都属于宋学,共同批评汉唐章句训诂注疏之学,而重视和提倡义理,这即是双方的相近处。如宋代易学之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以义理解释《周易》,就要求学者看王安石解《易》的文字。他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36]程颐提出,学者欲治易学,就须看王安石的《易解》等义理易学的文字,因为他们都属于易学的义理学派,都对汉易之象数学进行了批评。这反映了新学与理学在提倡宋学义理,批评汉学方面,具有共同之处。
从以上看,在经典文本上,新学与理学均重视“四书”之《孟子》,尤其是王安石改革科考,规定将《孟子》等列为兼经,成为科举考试必考之经书;不须尽用注疏,从制度上为兴起宋学及“四书”义理之学提供了保障。四书学的形成,尤其是《孟子》得列经书,王安石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大于诸理学家,亦是理学家所不可替代的。另外在对《周易》的解析上,程颐要求学者读王安石的解易文字,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新学对理学的影响;以宋儒义理之学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双方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理学受新学影响而互动的原因。
三、理学与新学的消长、辩难互动之启示
通过宋代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使得在两宋时期前后延续近百年之久的新学与理学之争,从整体上以新学的失势而告终。以杨时、胡宏、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新学的批评及政治上的原因令新学逐步丧失了其官学地位,而理学则在南宋后期成为官学,这种批判促使思想文化风向发生转变以及官方学术产生更替,使得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此至元明以降,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否定之说遂成定论,理学则一枝独秀。
理学与新学的异同、新学对理学的影响、理学对新学的批判,客观反映了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人们既要看到理学与新学对立相争的一面,同时也应看到二者相互影响、沟通融合而促进宋学乃至理学发展的一面。
理学与新学的消长、对立互动主要表现为在北宋时新学居于官学地位,理学此时属于宋学的重要一派,在与新学等各派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发展。二者相比较,新学可谓是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并用,内圣与外王同倡,但对经世致用和外王更加关注;理学则在不偏废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内圣与外王的同时,对道德性命和内圣更为重视。这与双方的学派性和特质相关。理学虽一度遭统治者废黜、禁止,但在南宋后期逐渐占据了官学地位。新学与理学消长、辩难互动带给人们的启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任何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都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合
新学和理学都曾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了宋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都曾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其思想理论也引起变化。
新学是“熙宁变法”的理论指导。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与变法相适应并为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是王安石提出的以《三经新义》为载体的新学思想,及在其他著述中阐发的新学理论。这基本适应了当时社会要求变革的需要,是新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新学在北宋时曾独尊于世,但由于北宋亡国,进入南宋后逐渐成为众多儒学批判攻击的对象,以致著述散佚,几乎处于湮没无闻状态。与此相反,理学虽在北宋时尚无很大的影响力,但至南宋其影响却处于不断提升中。由于理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基本适应,是针对汉唐注疏之学的流弊和佛教盛行冲击儒学的回应,是为了解决因旧日儒学发展停滞而带来理论危机并造成社会危机等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理学与新学理论的提出及其际遇,与其学派及其理论是否适应宋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密切相关。
(二)义利兼顾,情性相容
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虽有对立相争的一面,也有渗透融合、相互影响的一面,并非完全不相容。尽管新学重功利,理学重义轻利;新学讲善恶非性而在情,理学讲性善论,二者具有明显差异,但亦存在着融通相近的一面。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应重视二者相互影响、沟通融合的一面,树立义利兼顾、情性相容的观念,而克服各自理论的局限和偏差,以促进学术思想理论的完善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内圣外王,兼容并收
两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关系之所以表现出消长更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学与理学因其学术内在根基的差异,而对圣人之道与儒者修身的取舍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继而在“外王”与“内圣”的取舍问题上有着不同见解,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学重外王而兴起事功,理学则重内圣而坚持修身。对此,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37]二程偏重于义理心性之学的探索,并坚持内省的修养工夫,这也是宋学之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王安石则更为注重外在功效,他在与宋神宗的对话中曾语:“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38]执掌政权的王安石站在治理国家的角度,以通经致用的“外王”之道实践儒家先王经纬天下之意,其意本在救国利民,这放在北宋多灾多难的危急时刻原本也无可厚非。面对二者不同的态度,我们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双方各自的不同立场及不同思想理论的分歧,不能武断地认定孰是孰非。但对于内圣或外王某一方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另一方,都会带来一定的偏颇和流弊。儒家讲求修身成圣,并贯彻到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中,即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德才兼备。这无疑是十分全面的。
理学与新学之间在义利观上的差异和互动融合产生的结果是重义轻利的观念逐步占据了上风,但也不排斥对功利和客观物质利益的重视。理学由其重义轻利和提倡道德自律的特质而表现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新学由重视事功和社会治理而表现出重视外王的倾向,经理学与新学的互动而表现出义与利、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的倾向。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应将内圣与外王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兼容并收,而避免单纯重内轻外或只讲外在事功,不讲道德自律的片面性。我们探讨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克服两者的偏颇和片面之处,而吸取它们的长处,并将其结合起来而纠其偏,使其发挥应有的启示作用。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至今仍值得人们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借鉴。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朱人求
话语是关于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是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语言或文本而展开的社会交往与关系建构的实践。话语是哲学的表现形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话语,时代话语的转变往往意味着社会思潮的变换。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话语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是指对话语的语境、语义、语法、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性回顾与展望、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亲和性、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拓展、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操作等问题的追问与阐释,我认为,话语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将带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回顾
中国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它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说它年轻,它是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新学科。所谓范式转换,它指一种研究模式的根本改变,库恩把范式的转换理解为概念图式的更换,即“更换思维的帽子”[2]。回顾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西学范式和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率先提出中国哲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先秦时期群星灿烂,诸子百家蜂起,迎来了中国哲学最辉煌的子学时代。面对思想的失范和价值危机,诸子百家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共同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轴心时代”。西汉时期,汉武帝雄才大略,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哲学步入儒学独尊的“经学时代”,儒学也沦落为一种统治术,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哲学。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基本可以区分为子学范式和经学范式。[3]
所谓经学范式,是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各家各派恪守经典文化传统,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考订,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不敢阐释自我,追求经典阐释的客观性和承传性,中国哲学史上的汉学传统就是古文经学研究范式的最佳范例。所谓子学范式,是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各家各派立足时代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和思想阐释,追求思想的时代性和原创性,中国哲学史上的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子学范式的杰出代表,宋明理学中的宋学传统较为接近子学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经学范式与子学范式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子学中有经学,经学中有子学。当某一研究范式中思想的时代性和独创性胜出的时候,我们通常视之为子学,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就被认为是子学范式,而把那种追求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考订、注重经典的权威性和历史性的学问视之为经学,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就是经学范式。
(二)西学范式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接纳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但未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这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19年和1934年出版,后者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框架和典范。概而言之,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采用西洋思路与形式,拿西洋哲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自来学者的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西学研究范式。
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五步法[4])和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此为指导,借鉴西方近代哲学的书写范式,胡适建立了以“明变”“求因”“评判”为内容的哲学阐释框架。所谓“明变”,就是考察各家哲学思想渊源、相互影响及其变化的线索;“求因”,就是探索各家哲学思想兴衰变革的原因;“评判”,就是根据各家学说的影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就这样,通过纵向的渊源、流变的贯穿与横向的以哲人或每一个学派为中心的扩展,胡适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率先建构了一个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史阐释系统。在表现形式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明确区分了哲学与经学的疆界,对先秦诸子给予同样的地位;与经学的注释形式针锋相对,胡适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以经典的原文作为自己的注脚,中国哲学史彻底颠覆了经学范式而步入西学范式,从而获得了现代学科身份。《中国哲学史》尽管只完成了上卷,但是它完成旧有哲学史写作方式的解构,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制的先驱。
在严格的意义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坚信,中国古代哲学尽管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但有实质的系统,因此有必要运用逻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新梳理,“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5]他还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其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这种建构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选出类似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将这些内容重新组织起来,遂成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整个一生的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做这项精挑细选的工作,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人物、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在这三部哲学史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演绎。冯友兰还提出了遴选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基本标准:属上述哲学范围者、有新见且有自己系统者、有中心观念者,以及可作辅助材料的杂家之书,哲学家之人格、气质及思想社会背景均可作为哲学史史料。通过这种系统的整理与建构,中国哲学史旧貌换新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将中国哲学史纳入经济社会史解释框架中,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研究范式的构建。侯氏把胡、冯作为对手,认为胡、冯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然而,中世纪思想家研究,必须着重考察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7]侯外庐将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话明白地概括起来,就是: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和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来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8]侯外庐带着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进入学术领域,他所概括的是一个后来在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派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基本上没超出其框架。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倾向于将一种简单心物二元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解释原则和主要发展线索,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的历史,有失于简单化之嫌疑。
西学范式一统天下,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十分突出。金岳霖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像是一位美国商人写的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存在较大的隔膜感。冯友兰的“有似论”研究范式,则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9颜炳罡则认为,这种西学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砍掉了中国哲学的原典时代,使诸子之学成为无源之水;其二,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分解、打碎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整体性,使中国哲学由有机整体变成支离破碎的材料;其三,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集体失忆。简单地说,就是斩头,肢解,主体性丧失。[l0]如何走出西学范式,寻找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哲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三)多元化发展趋势
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统天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重写思想史、重写学术史的思潮。具体到中国哲学史研究,解释学、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大行其道,一方面这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也落入了西学研究范式的窠臼,因为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史有一件大事就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的问世。葛兆光指出,以往的哲学史都是围绕精英和经典写作“正统”思想的哲学史,这是哲学史很难改变的思路和方法。在冯友兰那里,就是以孔子和儒家、理学为历史线索,因为那些“非正统”的也就是非精英和非经典的东西里面,在冯友兰看来,确实很少有能够称得上“哲学”的东西。尽管后来我们中国的哲学史已经放宽了尺度,降低了门槛,但是,至今的哲学史叙述仍然是精英和经典为中心的,仍然在西洋哲学的尺寸和范围内,“抽取”和“选择”符合“哲学”的资料来叙述。但是,在古代历史和社会里,真正成为指导政治和生活的那些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中,还有很多不能被“哲学史”所描述的、一些“非正统”的东西,它们常常逃逸在哲学史的书写之外,那么,我们是否要用比较宽泛的、更有包容性的思想史来叙述呢?而那些导致思想与信仰发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与思想相关的社会生活史,是否也需要思想史来描述呢?因为思想史首先是历史,那种历史的场景、语境和心情,是思想理解的重要背景,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思想史是人们的观念与感受的历史”,“观念”可能可以被哲学史容纳,但“感受”就不仅仅是精英的和经典的,也包括一般民众的,不仅仅是理智思考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气氛构成的思想背景。[11]
21世纪伊始,学术界热衷于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家都普遍期望的中国哲学能说汉语、能“自己说自己”,走向多元、回归本土的研究范式,充其量还只是“哲学在中国”,还算不上“中国的哲学”,更没有形成标志性的成果和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需要一种“范式”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更多体现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不仅国内的研究深受现代主义思维范式的影响,而且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也不例外。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传统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解读中国古代哲学,例如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冯友兰的新实在论、贺麟的新黑格尔主义、牟宗三的康德哲学、唐君毅的黑格尔哲学等。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都表明了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依然没有上升到一种范式建构的自觉,中国哲学研究亟须完成“范式的转换”。如果没有这种“范式的转换”,将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导致远离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也就是说以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必然遮蔽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限制了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开放性理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埋没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独特和固有的东西。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学者用一种现代主义的模式来解读中国古代哲学,以削中国古代哲学之足适传统西方哲学之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范式的转换”,那么也将会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与时代精神脱节,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不能反映时代的精神,不能体现时代发展最新的趋势和需要。中国哲学如何回归中国,中国哲学如何接地气,如何接续上时代的脉搏,我认为,广泛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哲学话语势在必行。
二、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语法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第一次使用“话语分析”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他于1952年发表了“Discourse Analysis”一文,这篇论文通常被认为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话语分析的广泛应用于多种学科。这一时期,话语分析长足发展的标志就是两本杂志——《话语过程》和《语篇》,从此,“话语分析”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代表性学说有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尤其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代表。21世纪以来,话语分析研究仍在横向发展,即向着各个学科渗透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话语。
话语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但西方哲学界却对此持谨慎态度,以话语分析方法来分析哲学话语的成果相对较少。[12][就国内而言,目前仅见陈来先生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和几篇论文,陈来先生的论文对宋明理学话语的形成、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中对道学“中和”说、“穷理”说,对朱子的《仁说》、心说、道体说,陈淳的《北溪字义》,张栻的《太极解》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3],开始摆脱传统的以范畴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海外,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较早将“话语”理论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学研究。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他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作为思想学术事件,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14]艾尔曼把从理学到朴学的转换既看作一种儒学范式的转换,也视为一种儒学话语的转换——一种“从道德主义话语转向知识主义话语”“追求客观性的思潮压倒内圣理想”的革命。可见,话语的转换带来社会文化思潮的转换,也带来了儒学话语的变革。
基于话语分析方法的特质,我认为,话语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二者之间存在着亲和性。首先,话语源于日常生活世界,话语本身也指向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国哲学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强调认知与行动的一致性,恰好与话语分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其次,与儒家哲学立场相类似,话语分析非常重视话语与历史、现实生活的关联。“话语分析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对一个话语链或一团相互交织的话语链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或与现实相联系来分析;同时还应做到对话语链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做一些谨慎的说明。”[115中国哲学话语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是话语链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历史、现实不断交涉的过程。第三,注重哲学话语的具体语境的剖析。由于中国哲学话语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我们只有把哲学概念和范畴放进特定的时代和生活境遇中进行分析,才能诠释出其中沉默的“微言”和“大义”,才能达到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内在精神的真正把握。在这一点上,话语分析方法无疑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灵活性。
话语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实践,将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突破。范式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成熟的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方法、问题领域、解决问题标准的源泉,获得范式是这个领域成熟的标志。范式转换指知觉上的“格式塔[16]转换”,即抛弃原有的概念图式,抛弃概念本身进入到话语领域。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需要改变原有的以西学为主导的宰制性话语模式,由中国哲学自身话语完成自己的系统建构。具体而言,新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将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如下新的突破。
(一)从理论到实践
话语比范畴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为的关系往往比范畴、概念更直接。在社会行动中,话语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象(在心里预演或计划)或事后被理解。因此,有不少话语可以说是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James Paul Gee指出,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离不开社会活动。同样,没有社会活动也就没有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社会活动可产生和改变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因此,话语分析有必要研究人们如何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来进行社会活动、建立社会身份(identity)。[17]话语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反映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话语能对社会进行构建。话语具有建构知识和社会的能力,话语能建构物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建构活动,建构政治,建构身份关系,建构联系和符号系统等。
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和过程。“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准确地说明这个被称为话语实践的东西。……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而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8]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体现着权力和意识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既能促进社会再生,也能促进社会转型。NormanFairclough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分析则必须是一种多向度的分析方法,即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应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实践、一个话语实践和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19]
以“定性”话语的展开为例,“定性”是宋代道学的一个重要话题。针对张载因日常生活中外物的干扰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而发出的疑问,明道的精彩解答成就了一个经典学说——“定性说”。明道的“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绝非纯粹理论指导,它直接指向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何展开行动,或者说,认知的落实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朱子强调“存养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要有“存养”,要“功至”而后才有“得”,“得”的前提就是行动,它不指示纯粹的认知。西山讲“体”不离“用”,讲“以道养心”“以理养心”,对“用”和“养”的重视也是如此。简言之,道来自“伦常日用之中”,知“道”的目的是践“道”、行“道”,这正是儒家哲学的一贯立场。[20]同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仿,话语分析不仅仅是理论分析,它指向社会实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21]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22]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对概念、范畴的重视远远高于对实践的关注,有的甚至完全把实践排斥在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但话语实践一旦进入哲学关怀的视域,我们的哲学研究关注的不再是静态的思想观念,而是动态的话语实践及其历史发展进程。
(二)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话语就像“由‘社会知识库藏’连接而成的穿越时间的河流”,它从过去走向未来,它圈定了现在,并且以另外的形式继续流向未来![23]定性话语一旦奠定,它也由现在走向未来。话语分析也从传统哲学注重结论的静态分析转换为注重过程的动态分析,注重话语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把话语分析概念比喻为“采石场”,意思是说各学科皆可以从中提取原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这些材料是零碎的、无系统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把对知识和话语的考察比喻为思想考古,通过对知识和话语的深层历史的发掘,在现存的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的因子,从而揭示出被我们所忽视的珍贵的历史线索。简言之,福柯的知识考古的目的在于揭示出知识的先在结构,然后对话语的产生与发展、类型与规律等展开深入的分析。
明道的《定性书》是宋明理学的经典文本,它提出的“定性”话语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定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演化版本,并提出了许多远远超出本文意义的思想命题,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从主题上看,话语链是一个整体性的话语流程,它由一系列的话语片断构成。一般来说,思想的发展演进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通过对某一话语链的不断展开诠释、不断补充、丰富和深化其话语片断来完成的。从明道的《定性书》到朱子的《定性说》到西山的“定性论”,“定性”话语经历了一个由工夫论到效果论再到本体论的不断深化发展过程,显示出宋代“定性说”内在的发展理路。“定性”话语也由原来的性与情、性与心、动与静、定的工夫等话语片断逐渐扩展为“仁立义行而性定、理定于中、理即事、事即理”等话语,形成一个独特的整体性的话语流程。朱子和西山的创造性诠释,则体现了诠释的主体性、时代性、创造性和独立精神,体现了话语研究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为后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点和预设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当然,话语的诠释也与诠释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和人生体验密切相关。理解既是个体的行为,又是时代的行为。最后,当我们谋求某一问题的未来发展时,还必须注意当前话语链中主要话语的改变及其与其他话语链之间的相互关系。话语主题的转向也标志着社会思潮的转变。我们看到,当“定性”话语中的主题——“性”被置换为“心”时,“定性”话语的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定性”学说也完成了与心学主题的转换,它也意味着道学思潮开始向心学思潮的转变。
(三)话语与语境
话语分析特别注意话语语境分析,不同的话语在特定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James Paul Gee指出,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离不开社会活动。Gee非常重视结构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认知分析法,尤其强调语境的作用。其中,社会文化分析法把话语当作交际动作来分析,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由于语言交际涉及各种社会文化语境,我们不能单靠语言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来决定其意义,还要参照话语以及话语所产生的语境。话语和语境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话语受到语境的影响,同时也在影响、建立或改变语境。[24在相同的社会情境下,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社会文化知识的使用不同,话语也不一样。同一个社会文化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遵循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交际规则,交际才成为可能。
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25]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定性说”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透过明道、朱子和西山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道学家们对释老学说的排拒,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微言大义”的传统。当张载向明道请教“面对外物的诱惑如何保持不动心”时,明道的回答建构了一种师生的关系。朱子与学生的解读与问难既有思想家的成分也有师生的成分。西山则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把“定性”话语系统与帝王之学结合起来,在《大学衍义》中,“以道养心”“以理养心”的“定性”工夫直接指向的是帝王的修为,于是乎,一个在原初意义上仅仅指涉内在的身心修炼“定性”工夫也获得了外王的权力。
(四)从同一性到差异性、从连续性到断裂性
“话语分析”的主流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倾向,因而话语分析具有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注重差异性和断裂性的特质。话语分析把一切思想理论都平等地视为论述或陈述(一套说辞),把一切对象都一律地视为处于特殊语境之中的特定话语或带有特定价值预设即主观性的“陈述整体”,从而否定话语的确定性和真理性,从而否定真理的权威(其极端者如拉康(Jacques Lacan)干脆声言“真理来自误认”)。与确定性追求相比较,话语分析更为强调话语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建构性,重视揭露话语主体的言说或分析策略、政治动机、价值预设及其实践功能,致力于追究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传播和运作的社会化过程、作用方式和形态等,拒绝进行延续性的探索和原有思想史常用的那种影响分析,表现出一种对断裂和离散的偏执。福柯非常自觉地将他的“话语实践”即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加以区别。在他看来,传统思想史总是致力于在它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求“内聚力的原则”、共同点和一致性,最终总把矛盾消解在某种同一性之中,而话语分析则以描述、再现矛盾和差异本身为使命,它“描述各种有争议的空间”“不试图在矛盾中发现共同的形式或者主题,而是试图确定它们间离的尺度和形式”。[26其实,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绝对漠视连续性,在话语构型(discourseformation)中某些连续性他是不得不承认的。不过在分析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他更关注话语的断裂、强调历史的歧路和岔口,挑战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预定论和目的论。对影响、传统、进化、因果和发展这些传统中心概念的使用,福柯始终保持着警惕和反省。
当我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时,出于不同情境之中的同一话语往往具有不同的思想史意义。当程朱陆王在对“心”“理”“性”“命”“知”“行”等基本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话语片段)展开辩论时,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文本和境遇中它们的含义不尽相同,往往会陷入“鸡对鸭讲”的盲区。还是以“定性”话语为例,明道、朱子和西山有关定性的分析分别代表工夫论、效果论和本体论三种不同的理论类型,三位思想家以自己的独特理解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定性话语系统。如果是程朱理学一系对定性话语的理解有其内在的一贯性,那么,阳明心学对定性话语的界定则是断裂性大于连续性,从而完成了定性话语从理学到心学的创造性转换。
(五)从你—它到你—我
对话主义,顾名思义,即一种与述谓性的“独白”原则相对立的、而以交谈性的“对话”为宗旨的学说与思想。布伯对话主义哲学的思想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用我与你取向取代我与它取向。在传统西方哲学里,哲学研究的对象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我—它关系为其基本取向的。所谓我—它关系,即主体之于客体的关系。布伯则从我—它关系转向我—你关系。所谓我—你关系,即主体之于主体的关系。它不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会合”“相遇”关系,我不是把一切存在物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或伙伴性存在。第二,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在传统西方哲学里,立足于我—它取向的理论必然使一种主从性的原则作为其指南。它们或像古希腊宇宙本体论那样坚持“它”是支配者,“我”是从属者;或像近代康德理性本体论那样坚持“我”是支配者,“它”是从属者。与这类“父子型”的“还原论”或“基础主义”的哲学完全不同,布伯则坚持“关系是相互的”,关系双方并无主次、等级之分。第三,用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在传统西方哲学里,为跨越“我”与非我的“它”之间的鸿沟,哲学家往往诉诸和求助于某种中介性或媒介性的手段的建立。布伯则从间接关系走向直接关系,积极维护人与对象之间的非人为的天然联系。[27]
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一种求知(真理)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则是求道(至善)的哲学。“道”就是说话,就是对话。因而,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时,我们发现,这种对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早已出现。中国哲学有天之道,也有人之道,天地人为三才,三者相互沟通、相互对话。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古与今之间都在密切地对话,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成为中国哲学永恒的追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哲人之所以一开始就把“道”而非“理”作为其哲学的终极关怀,这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哲学的对话主义实质的最集中体现。中国哲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宋明理学又称道学,道是其最高的哲学范畴。在宋明理学中,道既是本体之道,也是道统之道、言说之道。宋明理学家都有自己的语录,通过对话来完成教学,通过对话来完成思想的建构与表达。在言说之中,你与我是对等的、当下的、直接的,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是交互的、同时性的,充分体现了对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人道与天道的对话与沟通中,理学家强调“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等,儒家的“仁学”成为沟通天人万物的中介,成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人伦的最高道德,它无所不包,生化万物,这样一种“仁道”充分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对话精神,通过“仁”的作用,每个人都不断消除小我、不断扩充大我,以同情心、同理心与他者对话与沟通,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实现天人一体,天人合一。
(六)从范畴、概念分析到话语(语句、语篇)分析,注重文本分析
尽管话语分析已趋向于避开对抽象或理想化结构的研究,笔者却认为,话语分析相对于曾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广泛流行的“范畴体系”研究仍有它的优先性。陈来先生指出,范畴体系研究“可以在范畴系统的一般特征方面显现出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不同,但范畴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具体问题的讨论,不是从具体的哲学讨论中理解范畴概念的意义,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的、笼统的说法上,而无法真正促进我们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具体讨论的理解。”[28]这里的“具体问题”即“具体语境”,对哲学话语的理解离不开它的具体语境,只有把哲学概念和范畴放进特定的时代和生活境遇中进行分析,深入研读文本,诠释出其中沉默的“微言”和“大义”,我们才能达到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内在精神的真正把握。中国话语分析应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由概念范畴的静态性分析走向动态性研究,注意话语与社会建构、话语与社会行动之间的有效关联,注重实践性、时间性、对话性、当下性是中国话语分析最为独特的地方。
道学话语分析打破了原来仅仅局限于哲学的狭小空间,注重哲学话语与其他社会话语之间的互动,注重哲学话语与社会建构之间的互动,使得道学话语研究深入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等相关研究领域,这一突破也使道学回归到其原有的“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恢宏格局,使道学研究不再被人为地肢解,从而回归道学的原初样态。但是这一改变也带来了话语分析的泛化和哲学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因而,在道学话语分析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文本与语境的关系、如何注重哲学话语的提炼、注重哲学话语的分析、注重话语的哲学特征也成为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三、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方法的操作途径:以道学话语系统(共同体)为例
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方法是对传统子学范式、经学范式、西学范式(尤其是范畴研究范式)等研究范式的承传、创新与超越,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中国哲学内部的关键话语与问题,它立足中国,与西方对话,凸现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如工夫话语与境界话语都是西方话语所无视的问题)。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旨在对中国哲学话语(文本、命题、实践工夫与境界)的语境、语义、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与西方话语分析方法有意疏离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与话语分析方法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哲学与其他领域。相当于西方话语分析,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方法更注重话语的过程性、时间性、建构性、实践性、你与我的对话、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联以及工夫话语所达成的境界。可见,话语分析虽然来自西方,但是中国哲学话语分析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工夫话语、境界话语、道德与政治的关联与对话等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这些新的话语理论形态,是对西方话语分析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话语分析方法是道学话语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方法论,该方法注重道学核心话语的分析,注重分析话语事件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把道学话语放进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脉络中展开研究。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操作路径如下。
首先,通过文本细读,确定所要分析的道学研究的核心话语。通过文本细读,深入文本,抓住文本的核心话语和时代核心话语展开分析,揭示被历史遮蔽的问题意识、时代主题及其解决之道,再现或还原思想史上遗失的重要环节。话语分析方法尽量用材料说话,暂时搁置主观价值判断,客观真实地揭示出文本特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旨趣。
其次,在数据库中进一步证实话语的核心地位。通过现有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韩国文集丛刊、日本儒林丛书等数据库,对道学核心话语进行检索,如果该核心话语在该文本和同时代及以后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几乎每一思想家都在反复讨论该话语,该话语的核心性就可以成立,该话语便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道学的关键话题。
再次,对该话语展开分析。深入文本和时代语境,对该话语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出该话语的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历史轨迹,阐释该话语的不同层次的含义,比较该话语在不同思想语境中、在不同思想家的视野中的不同含义并详细地分析其中的原因。话语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在话语分析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分析话语的社会建构、话语实践、道德与政治的关联性、工夫话语与境界话语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了解某一话语究竟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社会并取得何种效果,话语的社会化适应如何完成。
最后,在大量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建构道学的话语体系,分析其理论类型。其中,道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体认天理、理气先后、无极而太极、理即事,事即理、性即理、理气动静、心即理、理一分殊等),工夫话语(格物致知、主敬穷理、诚意正心、读书、静坐、体验未发之中、克己复礼、博文约礼、定性、慎独、拔本塞源、心统性情、事上磨炼、尊德性与道问学、操存省察、已发未发、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等),社会政治话语(正君心、出处、国是、教化等),境界话语(见天地之心、识仁、鸢飞鱼跃、孔颜之乐、曾点之志、自得、致良知、民胞物与、全体大用等)。在大量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构出道学话语系统,并分析其理论类型。[29]
道学话语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一个由道学家的思想与话语组成的话语共同体。陈来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较早关注道学话语系统的哲学家,他指出,所谓宋代道学话语的研究,是希望借鉴话语研究的方法,使宋代道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并使得对宋代道学前期发展的零散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获得方向和整合,从而使目前宋代理学的研究在单一的研究范式的状况下摆脱出来,走向新的、更为活跃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话语研究方法与西方话语理论关注文本与权力结构、符号与社会制度的联结不同,主要从学术陈述本身来看话语构型。从这方面来看,意义表达为陈述,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命题是陈述的形式化凝结;话语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来自命题、陈述的共同风格和共同主题,来自问题意识上的共识,也来自对关键概念使用的共同偏好,从而形成了话语体系。任何话语都是经过散杂、剔除、积累、集中的过程,才逐渐形成各个领域的话语系统。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传承,在中国又是和学派传承的意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道学无疑是一种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的过程,很值得加以细致研究,并总结、提炼出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30界定一个话语系统或话语共同体[31]的思想特质如下:(1)成员持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并且能辨识出他们之所以称为一个群体的一套超话语特征(意识形态);(2)社会化适应主要通过那些被认同的话语形式实现的(社会化适应);(3)一套被认同的话语形式是成员资格和身份旗帜或标识(话语形式);(4)界面关系由成员之间的话语或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话语规定(界面体系)(face systems)。[32]
在道学话语共同体中,道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特征)主要体现为七大法则。第一法则:天理(心)是最高的本体和原则,理想的社会是天理流行的社会。第二法则:个人目标是学为圣人,社会目标是回归三代。第三法则:尊崇道统,文化历史发展有它的连续性和周期性。第四法则:个体修养是获得个人幸福和社会认可的关键(为己之学、道德优先);个体是一个禀赋天理的实体,人性本善,但被欲望遮蔽,天理与人欲相互消长。第五法则:书院为道学社会化的主要推广模式。第六法则:内圣与外王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七法则:工夫话语及其实践是道学建构的中心。
道学话语的社会化适应包括:书院教育、讲会、社会教化和科举推动,其中书院教化是最基本的社会化适应模式。家族中的社会文化适应模式:父亲代表道德的权威。一个社会式话语系统所特有的教育和社会文化适应的理论是建立在其成员的善恶本性这一更为普遍的观念基础之上的。道学话语系统中的话语形式主要有:语录、集注、墓志铭、序跋、书信、行状、奏章、故事、说、诗文。理学话语的主要特征:公众性(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尊崇权威、先圣先王)、理性的、等级主义的(师生、圣凡、君臣、父子、上下)、群体主义的(或说道德主义的)、归纳的而非演绎的……道学话语系统中的界面体系区分为内部界面体系和外部界面体系,主要涉及道学内部的自我认同、道学群体内外的关系等。内部界面体系包括:公众话语(国家话语)、书院派话语(道学、心学话语等,具体分为湖湘学、婺学、永嘉学派、濂洛关闽、心学话语)。外部界面体系包括:非理学话语、异端(佛道)话语、其他话语等。
道学是关涉内圣外王的思想整体,是宋元明清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意识形态、界面系统和社会化适应模式。在应对佛老学说的挑战中,顺应宋代时代语境,道学应运而生。道学的本体话语、工夫话语、境界话语、社会政治话语等核心话语构成了其丰富的话语系统,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学话语秉承尧舜禹文武王周公孔孟的道统文化精神,坚持王道政治理想,倡导为己之学,关注“身心的修炼”(“哲学的修炼”),主张塑造道学新人格,书院教化是其社会化适应的主要模式。道学的工夫话语本身就是身心的修炼和哲学的修炼,是知行合一的工夫实践。其社会政治话语则建构了宋明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引领时代方向。在思想家的语录中,我们也能深深感受到道学家们直接的、当下的、平等的对话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力。总而言之,从话语建构模式上分析,道学上升为国家最高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话语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话语分析方法抛弃了以往以范畴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注重语篇和语境分析,关注话语实践,通过对道学的核心话语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道学的研究空间和理论内涵,一大批以前较少关注的道学话语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野。我认为,话语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将带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话语分析方法有它的普适性和独特性,它可以容纳西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和解释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理路,把概念、范畴视为话语片段、注重话语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注意到话语的差异性和断裂性,与先前的研究范式之间保持着连续性并不断推陈出新。话语分析方法能够回到中国哲学的原生态,回归内圣外王的整体性与统一性。话语分析方法注重本体、工夫、境界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其中,工夫话语是连接其他话语的关键,这一研究将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随着话语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一大批新的人物、新的文本、新的命题、新的话语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为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话语分析方法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它能充分表现中国人的生命情态、生命体验、生命境界和工夫实践,建立一种新的关联性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方法论的普及和推广,中国哲学研究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理论格局。
(原载《学术月刊》第48卷,2016年第9期,又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两岸协创中心、哲学系)“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
⊙陈逢源
一、前言
北宋诸儒昂然奋起,证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学发展历程中精彩的一页。濂、洛、关、闽相继而起,成就斐然,然而汇聚成果,有赖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重构经典工作[1],自此由理学入于经学,由讲论而及于经典诠释,成为儒学后续发展的重要事业,朱学传布与四书讲论,乃是一体之工作。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刘爚奏请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国学[2],理宗淳祐元年(1241)诏入学宫从祀,云:“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3]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颁《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定本。[4]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场试四书义,四书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宋代沦亡,元代继起,元朝既没,明朝接续,朝代不同,但都推崇四书,四书成为宋元以降学术核心。后人往往以政治威势来解释朱熹地位的提升,认为朱熹学术乃出于官方表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庆元党禁、局势汹汹之际,无法想象日后学脉得以延伸,学术得以拓展的情形,钱穆先生“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专以科举功令为说”[6],乃是相当深入中肯的说法。朱熹的坚持与门人后学的传播,印证义理,蓄积力量,由民间而及于官方,才是建立四书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7]南宋推崇朱熹学术,来自于既压复起,还以公道,恢复朱熹名誉;元代表彰《四书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取用乃是怀柔兼纳的手段而已,用意在于笼络士子。[8]同尊朱学,程度与用意不同,真正确立朱熹学术地位,主要来自于明朝态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旧,深有恢复传统的意义,考试以朱学为宗,已具气氛,然而贯彻帝王意志,以皇权威势整合歧异,建立朱熹为尊的经说体系,主要来自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等人纂修《四书大全》[9]。自此,朱熹成为学术宗主,四书成为后代最重要经典,《四书大全》成为明代士人成学、入仕最重要的经说依据。[10]《四书大全》的地位无可比拟,检视明儒言论,邹元标《愿学集》云:“惧学者溺于异指,令童习家学,见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图无疆之治。”[11]高攀龙《高子遗书》云:“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12]指出皇权政教一体之事实。清人陆陇其甚至直指:“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13]一学术,同风俗,明显可见政治操作的影响,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四书大全》,明代“官学化”的结果便是确立四书成为最重要经典。就经学发展而言,唐代《五经正义》整合义疏,完成经学统一,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之为“经学统一时代”[14];至于明代以《四书大全》统合元儒经说,皮氏以“积衰时代”[15]来称呼明朝经学,认为其为败坏学风的源头,立场明显矛盾。事实上,《四书大全》整合宋元四书讲论内容,一如《五经正义》统合汉魏以降的经疏成果。唐承汉魏,明继宋元,落实经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经典文本,具有同样的学术发展意义,然却深受误解!为求厘清,笔者针对《四书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核以《宋元学案》,撰成《〈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16],分析庞大征引来源,探究朱熹门人结集之后学脉、宗派而及于宗族乡里情怀不同阶段的传衍线索,得出结论:黄榦传学何基,北山一系称为朱学“嫡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具有由宋入元,巩固学脉正传的地位,也具有确立朱学内涵的意义。《四书大全》征引共计106家,其中名列《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其中征引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四书大全》建立诠释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得以溯及朱熹的关键,对于掌握义理方向深有启示。
二、北山四先生之四书学
朱熹之后,黄榦为学门领袖。[17]朱学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最为重要,他们代表了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统计朱熹门人籍贯分布,以第一传门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传门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传门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传门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传门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18]可见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朱学由福建往传浙江,影响日趋深远,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按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19]黄百家(1643~1709)按语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峯亦高弟也。双峯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20]
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成为宋元朱学传播的中心,从脉络渊源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华人,从父命师事黄榦,黄榦勉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于病革之际对弟子的期许[21]。何基撰有《中庸发挥》《大学发挥》《论语发挥》,惜皆亡佚。核其语录,云:
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敬五事则明明德也,厚八政则新民也,建皇极则止至善也;至学皇极,有休征而无咎征,有仁寿而无鄙殀,则中和位育之应,皇极之极功也。
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中《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22]
前者发挥四书义理,后者深化四书义涵,不论是扩之于外或是究之于内,皆是以四书作为学术核心,《四书章句集注》与《朱子语类》相参的路径,更是指引后世解读朱熹四书学非常重要的方向[23],无怪乎黄宗羲按语云: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犹不满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应聘讲,第恐无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则,若人者,皆不
熟读四书之故也。”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24]
何基守之既严,甚至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树立熟读四书的学门宗风,正是传自黄榦学术的证明。
何基学术传于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王柏关注四书态度不变,同样强调必须深究其内而不必旁伸于外,语录云:“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盖深求之于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25]即可为证。王柏崇信四书的立场并无改易,不过细节上显然已有不同的思考,“虽曰”一句已透露端倪。王柏重视四书经文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甚于朱熹,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中庸》当依《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庸说》二篇,以“诚明”以下别为一篇[26,相歧之处,皆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义理诠释的重点。然而王柏尝试从结构化解改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王柏有关四书类著作,有《订古中庸》《论语衍义》《论语通旨》《鲁经章句》《孟子通旨》《标注四书》等,可惜大都亡佚。重构四书文本,其实是延续朱熹思考的结果,只是背离朱熹说法,尊背注而求经,奉与违戾之间,立场不免令人疑惑。[27]
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柳贯《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云:
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语孟子考证》。[28]
补充名物,以备考证,用意在于补充而非阐释。《宋元学案》黄百家按语云:
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历时既久,思之甚深,诸多说法前后不同,甚至留有诸多待解之处,临终前为《大学》“诚意”章费心竭虑,更是人所熟知之事[30]。后人延续思考方向,尝试解决经典文本与注解诠释问题,乃是学术发展的常态。黄百家申明后人应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迹,无疑是通达而且正确的看法。金氏既守朱学之教,又发四书之义,有关四书之著作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其中《大学章句疏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皆收于《四库全书》之中。金履祥传之许谦,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矣”[31],皆是朱学核心要义,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许谦于四书亦颇有心得,黄溍云: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敷绎义理,惟务平实。每戒学者曰:“士之为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至于进修利钝,则视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舍其书,何以得其心乎?圣贤之心,尽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立言,辞约意广,读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贸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觉其意初不与己异,愈久而所得愈深,与己意合者亦大异于初矣。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约意广,深嚼有味,许谦推崇至极,由朱子而得四书义理,由四书而得见圣人,饶富义理进程,只是许谦发挥义理,并不墨守朱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33]重视四书,强调朱子,也留意缺失,补正朱注。[34]许谦有关四书著作有《中庸丛说》《大学丛说》《读四书丛说》。《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说》只是四卷残本,阮元从元板影录《论语丛说》三卷,又从吴中藏书家得元版《中庸丛说》足本二卷。[35]北山学脉由宋而及元,脉络清楚于此可见: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黄榦接续朱熹,设教讲学,推究义理,昂然挺立,成为宋元之际最重要的朱学重镇,一方面传播朱学,延伸学脉;另一方面阐释义理,开展议题,证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价值。诚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汉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于同也。[36]
以动态方式看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同之与异,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无古今,学无先后,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仆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37]。既不执拘定见,又深化朱学成果,四书遂有多元丰富之诠释内容。朱学由宋入元,由注进入疏解的阶段,学人在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辩证,不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深化,贡献良多,无怪乎明代章一阳以“正学渊源”为名,纂辑四先生著作《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38],视之为由宋及元四书学发展一个重要环节;清代戴锜亦以洙泗、濂洛、关闽、北山为一脉相承之体系,其云:
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洙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弗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歧途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干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39]
承袭濂、洛、关、闽,儒学得传,北山一脉学人地位于此可见。
三、《四书大全》征引之北山学脉
《四书大全》征引当中,名列《宋元学案》之《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征引情形如下:
征引量共计154条。北山一系学人的著作如今多数已经不传,《四书大全》征引其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朱子学发展当中,北山一脉具有衔接朱门与后学的作用,对此后人深有共识。吴师道为许谦《读四书丛说》撰序言之甚明,其云:
《读四书丛说》者,金华白云先生许君益之为其徒讲说,而其徒记之之编也。君师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师鲁斋王先生柏,从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门,北山则学于勉斋黄公,而得朱子之传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中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之后,不泯灭而就微,则泮涣而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41],对于后世建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方式,具有关键地位。明代《四书大全》援取疏解内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际朱学传布情形,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体系,未见何基言论,恐与何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42]的态度有关。至于王柏、金履祥、许谦当中,许谦征引最多,则是因为许谦为入元之后发扬朱学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学列传》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43]
许谦于元代,讲学四十载,授徒著录千余人,发扬朱学不遗余力,撰作既丰,成果斐然,成为《四书大全》重要征引对象,乃是理所当然。此外,北山一系学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欧阳玄、何梦桂(《四书通》《四书大全》皆作何梦贵)、方逢辰三人。欧阳玄,字原功,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博,列于“仁山门人”,有《圭斋文集》传世。方逢辰,字君锡,学者称蛟峰先生,学术“以格物为穷理之本,以笃行为修己之实,终身顾未尝有师承”[44,然而父亲方镕为“朱学续传”,家学渊源,同是朱学一脉:
彼亦有以颖悟为道,以卤莽灭裂为学者,其说谓:“不由阶级,不假修为。”以致知格物为支离,以躐等陵节为易简,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匪徒诬人,亦以自诬,天下未有一超径诣忽焉而圣贤者。
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学之博以积之,反之约以一之。[45]
重申格致之教,阐明穷理之功。由四书而六经,学而有序,归之于理,提供了一条有进程、有境界的儒学道路,体系俨然。至于易简之教,直接圣人,不仅是自诬,而且也诬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陆,立场至为明显。然而于学术推展,北山一脉学人彰显朱学,也有与陆学争是非的意义。何梦桂,字岩叟,学者称潜斋先生,与方逢辰为讲友,宋亡不仕,于艰困之中昂扬挺立,于家国沦亡之际慨然承传,在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具有以身体道的实践意义。[46]事实上,朱熹对于吕祖谦死后的浙东学风深有疑虑,永康功利之学、永嘉事功之学继之而起,一重实利,一重实事,然而求之于外的结果,违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为利所诱。为求厘清,朱熹特别表彰金华先儒范浚,并将《心箴》载于《孟子集注》当中,以乡贤前辈的名望对治后学驰功逐利的缺失,期许从功利之中回归于人心救赎。47可见往浙东开展乃是朱熹夙愿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学人由黄榦而继承朱学,另一方面浙东本身也有其学术传统,吕祖谦于丽泽书院和明招堂讲学,门人众多[48]。金华原就是众多学派思潮交会之地,陆学、永康学、永嘉学相互交流,深有调和色彩。《朱子语录》卷122载有朱熹之分析,其云: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而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吕祖谦兼纳博采,重史轻经,成为浙东学术的特色。然而朱熹认为根源不明,不免于关键处偏失,而重权谋,求功利的结果,则不免让人违弃仁义,最终让人误以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论语》救治偏蔽,强调在日用之际,在心念之间,高举仁义价值,坚持儒学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后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也是采取相同立场。朱熹对于浙东学风深有忧虑,于此可见。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为标题,说明朱熹于南宋尚虚、尚实学风之间,展开全方位文化论战,在南宋纷然并起的学术社群当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颇能说明朱熹学术的方向。[49]而门人黄榦往浙东传学,不仅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北山一系学人习之有验的结果,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熹学术最终得以胜出。只是学术面相更为复杂,朱学既从北山一系学人而深入于浙学,却也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诠释方式,学术既延伸又相互影响,也就无怪乎《宋元学案》黄百家一方面有“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有“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的观察,甚至于最后又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50]。黄百家出于浙学,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学于浙学发展中入于史,通于文[51],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四书义理愈加丰富,却也渐生歧见,其中矛盾,正来自于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的结果,尤其后人缺乏朱熹融铸义理、思之甚深的历程[52],各自揣想之下,于经文兴发议论,时见新意,也时有误解,甚至以纠弹朱熹说法作为个人学术成就,不仅混淆朱熹四书义理体系,也造成后人了解的困扰。此一情形,从后人论述当中可以得见。邓文原《四书通序》云:“近世为图为书者益众,大抵于先儒论著及朱子取舍之说有所未通,而遽为臆说,以衒于世。余尝以谓,昔之学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学者常患其不胜古人,求胜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53]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云:“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54]议论纷出,各立门户,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学人。“争奇取异”的结果,孰为正解,顿成经典诠释的重要问题。以朱熹为宗成为后人最终的方向,回归于朱学则成为建构诠释主轴最重要的诉求,此一主张于新安一系宗主乡贤前辈的气氛中开展[55],而于明代完成。明代四书官学化过程中,确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种整合学术的手段,也是尝试解决朱学传衍问题的途径。[56]发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书经说内容,于后人剔除歧出、化异求同的调整当中,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四书大全》申明朱熹四书体系,阐释朱熹诠释经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学术传衍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发展意义。
四、诠释转折与开展
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金履祥考证四书的内容,《四书大全》收录不多,有关名物训诂的资料,《四书大全》以张存中《四书通证》为主,原因所在,可以由其言“学者于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于《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着所出”[57]一窥端倪。考证后出转精,张存中以补其所出的角度,内容更为丰富,自然成为《四书大全》取用材料。至于王柏有关《大学》《中庸》文本结构的调整,也并未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材料当中,显然关注所在,已有不同。其次,以征引的数目分析,《四书大全》征引许谦材料,《大学》29条,《中庸》34条,《论语》22条,《孟子》33条,数目相当平均,然而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分量之悬殊,即可发觉其中有异。许谦有关《大学》《中庸》诠释成果,征引比例明显较高,如果与其他人加总计算,《大学》42条、《中庸》43条、《论语》30条、《孟子》39条,《大学》《中庸》征引比例明显偏多,至于《论语》则明显偏少。检核《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大学》《中庸》各有一卷,《论语》四卷、《孟子》四卷,共计十卷,《论语》《孟子》并无空缺,经过后人筛选拣择,《四书大全》似乎更加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诠释成果,而对于《论语》《孟子》部分关注不深。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四书进程、体系与境界的讨论,对于四书义理的兴趣,高于日用之间、事理之际的体悟。朱熹对于浙东学术曾有“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28]的针砭语,似乎也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当中。事实上,检视《四书大全》列举方式,小注以朱熹《语类》、《或问》内容为主,后文辅以弟子门人意见,最末则以“云峰胡氏”“新安陈氏”“东阳许氏”等元儒诠释作结。分析征引结构,前者可见朱熹讲论之义理方向,后者可见训诂与体例的补充,形成朱熹、门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经说体系,元儒经说部分,多数依循饶鲁、新安、北山三系为序,而许谦说法往往列于征引之末,借以阐明章旨的价值与意义。可见北山一系作为朱学由宋而及元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成为后人讨论的基础。后人赓续推究,进行更全面的四书义理思索,其中排序并非偶然。北山一系学人深化与开展之处,列举如下:
(一)推究工夫进程
训解经文为《四书大全》征引内容的大宗,收录北山一系学者意见也以此类说解最多。分析语意,也辩证义理,北山学人一脉相承,经典诠释有继承发展的现象。《大学章句》朱注“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引许谦、方逢辰云:
严密,是严厉缜密。武毅,是刚武强毅。以恂栗释瑟僩,而朱子谓恂栗者,严敬存乎中,金仁山谓所守者严密,所养者刚毅,严密是不麤疏,
武毅是不颓惰,以此展转体认,则瑟僩之义可见。
瑟是工夫细密,僩是工夫强毅,恂栗是兢兢业业。惟其兢业戒惧,所以工夫精密而强毅[59]。
金履祥分出所守所养有严密与刚毅的不同,许谦、方逢辰的诠释乃是承前发展。《孟子集注·告子上》“乡为身死而不受”章引许谦云:
三乡为身,北山先生作一读,言乡为辱身失义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为身外之物,施惠于人,而受失义之禄乎,可谓无良心矣。[60]
申明经旨,乃是引用何基说法,诠释层层累聚,于此可见。北山一系学人彰显经典旨趣,揭示其中要旨,最终往往归于修养工夫的思考。《大学章句》“《诗》云:‘瞻彼淇澳’”章引许谦云:
此节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谓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绪,谓先切琢而后可以磋磨,循序而进,工夫不辍。切磋以喻学,是就知上说止至善,讲习讨论,穷究事物之理,自浅以至深,自表以至里,直究至其极处。琢磨是就行上说止至善,谓修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直行至极处。瑟兮僩兮谓恂栗,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谓威仪,是德见于外者著。[61]
切磋琢磨,止于至善,许谦由知行两端,说明工夫所在,诚敬存乎中,尚不足有美盛德之形容,唯有达于至善,内恂栗而外威仪,融通内外,德容充溢表里。儒学有工夫、有进程,丰足饱满,由经典以入圣人之境,更有自信。《中庸章句》“诚者,天之道也”章引许谦云:
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择者,谓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谓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择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62]
以格物穷理说解经典意涵,择善而固执正是内外交养的结果。《大学章句》“所谓诚其意者”章引许谦云:
诚意只是着实为善,着实去恶。自欺是诚意之反,毋自欺是诚意工夫。二如,是诚意之实。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诚意之效,慎独,是诚意地头。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诚不诚,皆自为之。自欺者,适害己;不自慊者,徒为人。恶恶臭,好好色,人人皆实有此心,非伪也。二如字,晓学者当实
为善去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为也。[63]
以实释诚,途径直接明朗,为善去恶一出于诚,工夫纯由自己,无丝毫勉强,许谦确实掌握朱学的精神。《孟子·告子上》“操则存,舍则亡”章引许谦云:
浩然章论养气,而以心为主;此章论养心,而以气为验。曰志者气之帅,故谓以心为主。曰平旦好恶与人相近,故谓以气为验。集义固为养气之方,所以知夫义而集之者乃心也,养心固戒其梏亡。验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则气也,彼欲养而无暴,以充吾仁义之气,此欲因气之息,以养吾仁义之心。两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尝不同,而气则有在身在天之异,然未始不相为用也。[64]
这番话对心与气的关系言之甚详,养心验气,养气由心,唯有心气交养,才能仁义充盈,指出儒学极为重要的修养方法,以及朱学重要学理内容,诠释深切到位。《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章引王柏云:
“善推其所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65]
孟子开展仁义,正是善推其所为,学问在此,修养亦在此,儒学精神于此显豁,可见经典阅读的深入与精彩。当然其中也有理解偏失之处,《中庸章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章引许谦云:
程子谓不偏之谓中,固兼举动静。朱子不偏不倚,则专指未发者。[66程子兼有动静,朱熹仅言及未发之中,许氏辨别程、朱有不同的诠释重点,但对于朱熹融静于敬,涵养更密的思考,体会不深。《四书大全》载录朱熹弟子陈淳之言,云:“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可谓确而尽矣。”67朱熹取程子之说,推而及于内外动静,内涵更为周延细腻,许氏未能详究朱熹中和之悟的进程[68,观察并不深入。《大学章句》“物格而后知至”章引许谦云: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谓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揍合将来,遂全其心而足应天下事矣。[69]
“而后”既是顺序之词,也是一种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关乎工夫进程,兹事体大。《四书大全》引朱熹之说云:
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着“而”字,则是先为此而后能为彼也。盖即物而极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无不至。吾知无不至矣,而后见善明、察恶尽,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诚。意无不诚矣,而后念虑隐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70]
格物乃是修养的关键,即物穷理,知明而意诚。就工夫而言,朱熹有深刻的思考,所谓“先为此而后能为彼”,正是强调其中顺序不可紊乱,以及学术进程的安排,此为朱学工夫论的核心。然而浙东学术贵通达,许谦对此却有一种转折性的诠释,强调“致知力行”并进,于是一物之格,诚意、正心、修身乃是同时进行,最终期许逐渐理会,全其心以应天下之事,于是工夫所在,一次到位。说法是否符合朱熹原旨,有待深入讨论,但对于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因此“终身无可行之日”的逻辑问题,遂有可以解决的方向。
(二)阐明境界所在
朱熹以一生建构四书义理,如何确立有效理解,乃是后人研究的首要之务。《中庸章句序》引许谦云:
《章句》《辑略》《或问》三书既备,然后《中庸》之书,如支体之分,骨节之解,而脉络却相贯穿通透。[71]
此一方法与黄榦强调直究原典,以《章句》为研读根本的方式不同。72黄榦标举的方法,目的在于避免淆乱,然而浙东学术重视文献,更加留意考据的趣味,取径开阔,以《章句》为本,佐以《辑略》《或问》的研读方式,有助于了解朱熹思考进程,转折之间,《中庸》义理得以显豁。有关研读方法的指引,也见于《读中庸法》引许谦云:
《中庸》《大学》二书,规模不同。《大学》纲目相维,经传明整,犹可寻求。《中庸》赞道之极,有就天言者,有就圣人言者,有就学者言者,广大精微,开阖变化,高下兼包,巨细毕举,故尤不易穷究。[73]
《大学》言纲领,《中庸》明境界,研读方式,朱熹原就有安排,其云: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74]
《中庸》标举天道、圣人,期许学者有以继之,许氏所言确实符合其中旨趣。至于《章句》《或问》相参方式,提供深入朱熹义理思考细节,《中庸或问》引方逢辰可以为例,其云:
《或问》中旧说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句,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盖谓有主张是者,而实未尝有所为耳。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直谓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二说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谓鸢鱼之飞跃,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处,勿正心,谓无勉强期必,非有心着意也。活泼泼地,是指天理呈露处,此朱子旧说之意,就鸢鱼上言。今说却就看鸢鱼之人上言,谓就费视隐,必自存其心,则道理跃如矣。朱子谓只从这里收一收,这个便在,朱子两说皆精,但前说恐人无下手处,故改从后说之实。[75]
朱熹为免蹈空入虚,前后之间,趋之于实,朱学最终精神的趋向所在,于此可见。事实上,浙东学人强调文本结构,《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章引许谦云:
此章专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细微处不合道,而于远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势必当如此。故于费隐之后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谨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则言正己不求于外。此章则言自近及远,是言凡行道皆当如是也。引《诗》本是比喻说,然于道中言治家,则次序又如此。[76]
《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费而隐”[77,循此而下,第十三章阐明以恕行之,第十四章说明正己不求于外,第十五言行道自近及远,层层而进,彼此衔接,各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申明由近而及远,日用之间,道无所不在。许氏善用文学分析手法,章旨可以据此而得。此外,比较两章之间手法,也可以了解经旨所在。《中庸章句》第三十章朱注“言天道也”引许谦云:
二十六章言圣人至诚,与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则圣人之盛大自见。此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道,自万物并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则圣人之大自见。前章则引文王之诗以结之,此章则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礼,无非形容圣人之德也。[78]
圣人与天地同道,许谦比对《中庸章句》第二十六章、三十章,同样是言天地之盛大,以见圣人之盛大,铺排方式相同,至于二十九章引《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79为结,三十章则以“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80]破题,前者为文王,后者为孔子,圣圣相承,彼此衔接。至于以孔子作结,《中庸章句大全》“仲尼祖述尧舜”章引方逢辰云: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书之末,以仲尼明之。[81]
可见文本具有内在的肌理脉络,经典意义结穴所在,揭之而出,遂能彰显结构用意。经典本身原就有圣圣相承的线索,既承继而发展,又遥接而发挥,圣道境界遂有其理据。朱熹分享经典阅读经验,言“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却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821。读经必须从章句文字的语意层面,深入于文本结构当中,推敲全篇旨趣所在。浙东学人延续朱熹思考方向,诠释更趋务实。《大学章句序》“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一句引许谦云:
规模节目,以三纲八条对言,则三纲为规模,八条为节目,谓八条即三纲中事也。独以八条言之,则平天下为规模,上七条为节目,平天下是大学之极功。然须是有上七条,节节做工夫,行至于极,然后可以平天下。[83]
以《大学》而言,三纲为规模,八目为节目,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84],两相搭配,乃是极为适切的诠释。但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延伸,离三纲而言八目,以平天下为规模,格、致、诚、正、修、齐、治为节目,不无可疑,毕竟缺乏明明德之根本,八目不免有外驰之弊。或许对于元儒而言,平治天下乃是儒者事业所在,也是儒学规模所在,儒学境界于经旨当中获得启发,外王事业也是儒学的究竟,因此寄以无限的期许。许衡留意经文结构,于是将规模与节目视为境界与进程,将三纲与八目视为两个独立文本,然而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外王事业,于此可见。
五、结语
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义理推究深微,四书成为学术核心。在宋元学术纷出之际,北山学人证明朱学价值,饶富学术发展意义。《四书大全》征引的仅是部分内容,自然无法代表全貌,然而重视工夫,强调境界,北山一系学人融通经学与理学,厘清四书文本内涵,在经典诠释当中彰显朱熹学术价值。经由北山一系学人的努力与尝试,明儒四书经注诠释体系才能完成。只可惜北山一系学人为朱学嫡子,然而承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并不明显。《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章引胡炳文云:
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极功。学者不知所向,则非有志于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则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趋向之正,造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为明道矣!真知明道,则真知尧舜以至孔孟者矣!善乎勉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85]
胡炳文乃是新安一系的学者,黄榦推崇朱熹为百世而下心领神会之人,北山一系学人经由黄榦溯源于朱熹,以身份而言更为纯粹,对于朱熹道统应有进一步的说法,但是征引情形并不明显,相关论述几乎集中于新安一系学人。元代不同宗派,不同学术系统,彼此相互竞逐,《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或许出于明成祖排除明初开国浙东学人势力的一种手段。[86]然而学术积累,北山一系学人诠释心得,终不得掩,观察征引情形,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黄榦彰显朱学,以传道为己任,以影响层面而言,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是宋元朱学传播中心,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
其二,朱熹从北山一系而深入于浙学,却也不免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倾向,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其结果,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影响愈深,也难免渐生歧见。
其三,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北山一系经说以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四书大全》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的诠释成果,对于《论语》《孟子》关注不深。
其四,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推究深微,《四书大全》征引特别留意儒学修养工夫,也关注儒学境界所在,贯串绵密,融通经学与理学的思考方式,奠定了义理开展之基础。
其五,黄榦表彰朱熹,四书、朱熹、道统三位一体,北山一系学人虽然为朱学嫡子,号为正传,然而《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而延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的,却是新安一系学者。
北山一系学人乃是传承朱学的重要学脉,也是《四书大全》建构经疏体系的重要基础,只是几经转折,分析结构、推究含义,遂有不同的思考,后世儒学重要主张,隐然已见于《四书大全》征引北山学人的言论当中。工夫期许知行并进,境界强调内圣外王,对于明代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清初经世致用之学,饶有启发作用,更可见北山一系学人深层影响。只是无可讳言,《四书大全》征引内容既多且杂,梳理不易,分析脉络,尚多疏陋,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原载《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
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
⊙〔日〕川原秀城 申绪璐 译 吴震 校
朝鲜朝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派大军侵略朝鲜。这场战役(包含休战期)前后长达七年(1592~1598),此即倭乱(文禄、庆长之役)。另外,在仁祖期间,后金(清)军队两次(1627、1636~1637)入侵朝鲜,此即胡乱。倭乱、胡乱的战祸是未曾有过的,使得朝鲜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朝鲜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的朱子学权威开始下降,其对政治社会的思想影响力也已大不如前。
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因为社会变动而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上的回应方式。其一是肯定传统价值,重视历史传承,对于固执于“社会模型”的保守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进行重新组合与强化;另一种则是绝对地信赖理性,正视“社会现实”,实行革新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的变革。在笔者看来,在朝鲜朝后期,前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统治思想的绝对化,后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的相对化。
在朝鲜思想史上,最先有组织地推进朱子学的绝对化(教条化),是刚进入朝鲜朝后期时出现的宋时烈(1607~1689)。宋时烈重视朱子学理念的原理和原则,并将其绝对化,即:(1)通过理论整理以证明朱子学整体的正确性(无谬性);(2)作为社会全体绝对的指针进行广泛的普及;(3)回归根本的理念并追求严格的应用,以此克服朝鲜社会的危机。宋时烈自定的使命即“明天理正人心,辟异端扶正学”(权尚夏《尤庵先生墓表》)。宋时烈政治思想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可由朝鲜朝后期的政界与学界中老论与宋时烈学派的持续兴盛得到证明。
另一方面,革新主义的朱子学者面对倭乱、胡乱之后的社会思想危机,正视两班社会的矛盾,拒斥教条(独断学说)而将朱子学相对化,试图通过推进思想的自由和灵活的社会应对以克服深刻的危机。这是因为朱子学业已丧失活力并严重衰退,很少有人还会原封不动地信奉其教义,也很难再对体制性教学的作用寄予期待,而更高层次的“义理”本身则与此相反,乃是天下共有之物,拥有无穷、无限的可能性。
尹䥴(1617~1680)与朴世堂(1629~1703)等人,与宋时烈一样正确地认识到朱子言论中的同异矛盾,以朱子定论(主要是《四书集注》中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再考察,或者通过对朱子定论与其他朱子言论进行对比,以此提出与朱子定论不同的观点并主张自身正当性。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将朱子学相对化、灵活化。另外,郑齐斗(1649~1736)则认真地研究阳明学,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四书解释等方面。虽然不能确定他是否是阳明学学者,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在朱子独尊的朝鲜社会中,朱子学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化。
初期的革新主义者超越以往的范围,构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但他们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论,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看,都是不充分的。具备思想实质的真正的社会改革论,还要等到朝鲜朝后期18世纪实学(朝鲜实学)的登场。实学之名原是指向实用之学问,然而朝鲜朝的实学家一方面重视保持朱子学的框架和严格区分传统与异端;另一方面又主张即使是异端之言,若有可观之处,亦必须学习,并且鼓励超越朱子学的范围(甚至不避攻朱),对于包含实用之术的广泛领域进行研究。[1]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分析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以期阐明朱子学相对化的内在实质。[2]具体而言,分析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与洪大容(1731~1783)的朱子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互相纠缠的思想性格,即宗朱与攻朱的奇妙混合(既保持强烈的思想正统意识,在本质上对异端思想采取非宽容之态度的同时,又积极地研究异端思想,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朱子学体系),以期论证这样一个问题:西学在作为朱子学相对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朝鲜实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李瀷的学术
李瀷,字子新,自号星湖,祖籍为京畿道骊州,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朱子学者、西学者之一。[3]
(一)强烈的道统意识与异端的西学研究并存
李瀷的一生,经受了17世纪末激烈党争的冲击,他是经常生活在政治剧变之阴影中的两班知识人。其家族为科举合格者辈出的南人名门,曾祖父李尚毅为议政府左赞成,祖父李志安任司宪府持平。其父李夏镇亦为司宪府大司宪,肃宗六年(1680)遭遇了南人大黜陟(又称庚申大黜陟)事件,随之失职而被流放到平安道云山。
肃宗七年(1681),李瀷出生于其父的流放地。第二年,其父李夏镇去世,李瀷随母亲移居先祖坟墓所在的京畿道广州的瞻星里。李瀷资质聪颖,优于常人,但是生而病弱,无法外出就学,其学问主要得益于稍稍年长的仲兄李潜。
但是仲兄李潜于肃宗三十二年(1706),以老论金春泽等人企图危害王世子为由而上诉,要求撤换老论的右议政李颐明,引发了肃宗的愤怒,拷问之后而被杖杀。仲兄因党争而惨死,李瀷为此而受到极大的冲击,失去了立身出世以及关心世事的意愿,从而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学习,此后作为在野的学者而专心于读书和著述。英祖三年(1727),虽被推举为缮工监假监役,他力辞而无意仕进。英祖三十九年(1763)去世,享年83岁。
李瀷的学问大致由三方面组成:(1)在吸收朝鲜朱子学(性理学)一派的李滉(1501~1570)思想的同时,(2)对于欧洲传来的新知识(西学)亦有正面的评价,并以此展开了新考察,另外,(3)受到柳馨远等人经世论的影响,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主张。[4]
李瀷学问的根本在于性理学,[5]其学统属于退溪李滉→寒冈郑逑(1543~1620)→眉叟许穆(1595~1682)传承的畿湖南人一系。但是,李瀷不止于将自身的师承系于李退溪,而是从个人内心出发,十分仰慕退溪的学德。因此,李瀷模仿《近思录》编集了收录退溪言行的《李子粹语》,以及为退溪的四端七情论辩护的《四七新编》,从退溪的遗集中分类抄出与礼相关的书札而编纂了《李先生礼说类编》等。另外,李瀷希望通过研究经书和性理学书来把握真理,以供社会之实用。这一点可由保存下来的有关《诗经》《尚书》《周易》三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以及《家礼》《近思录》《心经》《小学》等大量读书笔记得以证明。《诗经疾书》《书经疾书》等便是此类著述。
李瀷将继承与发展朱子学说作为其一生的志向,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如果反朱子学者的异端言论中有不得不看之处,亦应当学习。他积极地学习西学,果断地利用西学知识来解释儒家经文,并提出多种社会改革论。真正的学者必须为了振兴正学而批判异端,但是李瀷不受此拘束,而是在了解异端的同时,视西学研究为学者之当为而予以肯定,不得不说这是作为朱子学者不应有的态度。
在维持朱子学所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之同时,对于必须拒斥的异端却予以宽容,关于这一点或许应当做这样的解释最为稳妥:“这是一种承认其他思想也有部分价值的有限的多价值主义。”[6]
(二)星湖西学的概要
朝鲜朝景宗四年(1724)春,慎后聃拜访李瀷而了解到所谓“西洋之学”,于是,多次就西学问题,与星湖发生了论争,相关记录便是《遯窩西学辨》。该书大致由《纪闻编》《灵言蠡勺辨》《天主实义辨》和《职方外纪辨》所组成。《纪闻编》的撰写目的在于介绍星湖西学的概要。
基于慎后聃的《纪闻编》,可以看出李瀷西学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虽然李瀷自身最终否定基督教神学,但并不认为西教是耶稣会的阴谋(“张伪教而陷一世”),西学以外的西教也可成为分析考察的对象。例如,尽管慎后聃批评“天堂地狱之说”等西教理论的荒唐性,但是李瀷却介绍了西学的“实用处”(科学内容)强调其有用性,拥护“利西泰之学”。这与后文讨论的洪大容认为西教不值一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特征是,将脑主知觉说(“头有脑囊,为记含之主”)与三魂论(“草木有生魂,禽兽有觉魂,人有灵魂”)作为西学的核心命题。[7]甲辰(1724)春,针对慎后聃的西学“以何为宗”的问题,李瀷自己以“论学之大要”提出上述二说,可见上述说法是可以确定的。另外,戊申(1728)春,慎后聃曾对李翊卫提及,李瀷认同这样的命题。
所谓脑主知觉说,即“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李瀷《星湖僿学类选》的《西国医》以汤若望《主制群征》(1629年刊行)为依据,论述了“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这一观点,将西医的脑主知觉说与东医的心主知觉说予以折中,认为在人类的两大精神作用中,“感觉与知觉的作用在脑,思考与理性的作用在心”(“觉在脑而知在心”)。另外他主张一身流行的形气粗大,主思的心气(心脏之气)则极其细微,而它们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所谓“三魂论”,这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灵魂论,认为草木只有生魂(生长之心,anima vegetabilis),禽兽有生魂(生长之心)和觉魂(知觉之心,anima senseitiva),人有生魂(生长之心)、觉魂(知觉之心)和灵魂(理义之心,anima rationalis)。若将《星湖全集》卷四十一的《心说》、卷五十四的《跋荀子》以及《星湖僿说类选》的《荀子》合而观之,毫无疑问,李瀷所说的三魂论的论据与《灵言蠡酌》《天主实义》的灵魂论以及《荀子·王制篇》的“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有义”非常相似。
第三个特征是,李瀷认为“天文筹数法”“星历象数学”是“发前人所未发”或“有前古之所未发者”,极其称赞。[8]乙巳(1725)秋,李瀷解说了十二重天、温带凉带、地圆、日月行度、去极远近等,并记述了日月食预报的正确性。另外他还指出,郑玄的“地厚三万里”与西历的“地围九万里”是暗合的。
李瀷对于西欧数理科学的称赞在《纪闻篇》以外的很多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比如根据安鼎福《天学问答》的附录,李瀷指出西欧的“天文推步、制造器皿、算数等术,非中夏之所及也”。尤其称赞“今时宪历法,可谓百代无弊”,“西国历法,非尧时历之可比也”。[9]
(三)星湖的四端七情论
李瀷的心情论、四端七情论是退溪以来朝鲜朱子学内在发展的优秀成果[10],但同时必须承认其性理学的命题中也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李瀷的四端七情论,虽说是沿袭李滉以来的理气范式,但是吸收了奇大升(1527~1572)开始倡导而由李珥(1536~1584)集大成的心发的理气不离的基本原理,并借此重新解释李滉主理的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具体到心情论所讨论的心之机能与构造的问题,李滉以宋代张载“心统性情”为理论根基,从“性”“\情”观点出发论心,而李珥受元代胡炳文“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大学章句大全·经一章》小注)的启发,与性、情一样重“意”。对此,李瀷则在性、情、意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论点的变化以及论题的扩大。这与朝鲜朱子学的不断扩大进而发生变质的发展趋向是吻合的。
1.三魂论的影响
李瀷为了证明李滉理气互发的合理性[11],提出了严格区分知觉与思考的公私二情论,即将人心(七情)归属于“知觉之心”(私情),而将道心(四端)归属于“理义之心”(公情)。另外,为了论证源自公私的人心道心说的合理性,通过草木之心、禽兽之心与人类之心的对比,分析人所具备的心之构造。[12]
在《心说》一文中,李瀷认为虽然土石是无心的,然而“人者,较之于草木而均有生长之心。较之于禽兽而有知觉之心。其义理之心,则彼草木禽兽所未有也”。又说:“至于人,其有生长及知觉之心,固与禽兽同,而又有所谓理义之心者。”在星湖看来,植物、动物与人类之心具有如下的分层构造:
草木仅有生长之心
禽兽有生长之心与知觉之心
人有生长之心、知觉之心与理义(义理)之心在李瀷看来,知觉之心为人心,即人情,而理义之心为道心,即四端。
李瀷所说的草木、禽兽、人类的进化分层的心论,其构造非常独特。显而易见,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在内容或构造上都基本相同。另外如前所述,李瀷曾经通过《灵言蠡酌》与《天主实义》学习了欧洲哲学的心情论(三魂论)。由此可以断定,李瀷的公私心学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2.脑囊论(大气小气说)的影响
李瀷在其四端七情论中,论述了心情的发现路径与感应路径,其发现路径由道心(四端)的理发(理直发)与人心(七情)的气发(形气发)的互发二路所构成;相对于此,感应路径则是伴随发现路径而来,两者都属于理气共发的“理发气随”一路。
李瀷提到,首先,性“感物而动”,此时生发作为“性之欲”的情(《礼记·乐记》),四端、七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吾性感于外物而动,而不与吾形气相干者,属之理发。外物触吾形气而后吾性始感而动者,属之气发。”(《四七新编·第八》)“四端不因形气而直发,故属之理发。七情理因形气发,则属之气发。”(《四七新编·重跋》)在李瀷看来,理发意味着理的直接发动,与此相对,情的发动即气发是外物触及形气即身体,从而产生身体感觉(由外部刺激产生的身体感觉),再传达至心,最后理(或者思考、理性)发动(可参见出于李瀷之手的《四端七情图》,如右图)。李瀷所说的气发,由触及形气(身体)而生发,故以此命名,但是从发生的主体来看,则依然是理发而已。
在李瀷看来,心的发现路径有理发(理直发)与气发(形气发)两路,但是紧随发现路径而来的感应路径则只有理发气随(理应气随)一路。他说:“理发气随,四七同然。而若七情,则理发上面更有一层苗脉。所谓形气之私是也。”(《四七新编·重跋》)“心之感应,只有理发气随一路而已。四七何尝有异哉!”(《答李汝谦庚申》)关于星湖心学的“心发”构造,可以表示如下:
四端=道心(道德的情感)理发气随
七情=人心(由知觉而生的情感)生于形气之私→理发气随
须注意的是,在李瀷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的心发说当中,就发现而言,讲的是理气互发;就感应而言,讲的则是理气共发。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理论上的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李瀷指出,七情气发之气是指形气,与理发气随之气并不相同;所谓七情之气发,是指理发气随的知觉依形气而发。他说“气有大小。形气之气属之身,气随之气属之心。形大而心小也。”(《答慎耳老辛酉》)这是说,形气(一身混沦之气)与心气(神明之气)在大小差异及灵妙上的不同,而其作用也是根本不同的。
尽管李瀷的二情论可以说是以二情的绝对区别为其特征的,但是之所以说二情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最终的感应路径(思考)虽然一样,但是其发现路径(知觉与思考)却是不同的,故而知觉与思考的作用部位是有差异的。李瀷自身虽未明言,但是不得不说一种心理学的命题,即如下的心理二重构造乃是其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细微的神明之气相关的构造是“心↔思考↔理发气随”,与缺乏灵妙的粗糙形气相关的是“脑↔感觉↔气发”。
如前所述,李瀷通过分析《主制群征》所说的西洋医学知识,了解到气有
图1《四端七情图》大小粗细,而大小的不同导致各自机能的差异;断定感觉与思考是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上述两个命题,都与星湖的人心道心论非常吻合。星湖在构建其公私心学之际,很有可能是援用了这两个命题,以此作为其思想的前提。这是因为心发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之模型,即“知觉之心”的一身流行的形气为大,“理义之心”心气为小,同时感觉与思考是来自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这完全可以对应于西欧的医学理论。
3.中西会通与西学的理论优越
李瀷作为朱子学学者,他坚信儒学在整体上的正确性(“无谬性”),同时作为西学者,他所追求的是更高层次上统一中西两学,即17~18世纪西学研究者共同的理想“中西会通”。因此在他的论述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从东亚视角出发,来实现东西理论的无矛盾统一,并以经学理论为优的立场来加以整合或折中。在上述的四端七情论以其及论文《天行健》和《跋职方外纪》当中,我们便能看到这样的主题。
(1)《天行健》
《星湖僿说·天地门》中的论文《天行健》根据《易经·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说明西欧传来的天动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此天动认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三垣二十八宿天、宗动天等,都是围绕宇宙中心的不动的地球而公转的。
李瀷认为,《广雅》载“天之距地二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则说“五亿三千三百七十八里有奇”。两种说法,何者为是,尽管今天难以确定,但是两说都主张天是巨大的物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天既然是巨大的物体,因此不可能一日一循环(“一日一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周即对“天动”提出疑问,其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庄子·天运》)因为在理论上,即便是“地动”说,也能很好地说明天文现象。
但是,中国宋代朱子对于同样的问题,指出“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即天一日一转,地亦随之而转,而不及天运一度13],最后说“今坐于地,但知地之不动。”(《朱子语类》卷八十六)[14]朱子的观点(据星湖,这是对“地动”说的否定)亦须深入思考。
进而言之,圣人著述的《易经·乾卦·大象》中有“天行健”之说。据此,由于“圣人无所不知”,因而所谓“天行健”,即指天之自动而不容怀疑,李瀷指出:“可信且从之”。
要之,李瀷以经书的“天行健”一句来驳斥科学命题的“地动”说[15],竭力宣扬当时已成西学定论的“天动”说。
(2)《跋职方外纪》
《星湖全集》卷五十五的《跋职方外纪》,以《中庸》的子思语为根据,主张地圆说的合理性,也提出了同样的论述。《职方外纪》是意大利人耶稣会士艾儒略增译、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1557~1626)所汇编的五卷本世界地理书,完成于明天启三年(1623),收于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另外一人李之藻(1565~1630)编纂的《天学初函·理编》。
李瀷的《跋职方外纪》,开首便引用了《中庸》第26章的“地,振河海而不泄”。[16]李瀷指出,子思的说法(前半部分)意味着,并非海洋在陆地中漂浮,而是陆地纳大海于自身。即便在溟海或渤海之外,海洋必然有底,其底部皆为陆地所构成。这与西洋人详细论证的说法相契合,没有丝毫差异。
大地将海洋收于其中而海水不外泄,这是因为大地处于天圆的中心位置。由于天由东向西一日一周,所以处于天之运转中的物体,势必因其向心力的作用,而不得不向中心集中。即所谓“在天之内者,其势莫不辏以向中”。地既不下坠也不上升,上下四周皆以地为下、以天为上,其原因是一样的。[17]
由海洋是附着于陆地的观点,便不难推出“地圆”的命题。因为若向西航行至极,终究将再次进入东海(所谓“航海穷西,毕竟得出东海”)。而且,如果在航海的途中观察星象,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天顶亦各有差异。因为南界星可以在低纬度看见,而无法在高纬度看见。
《职方外纪》记录了西洋人真实的航海记录。例如其中记录了阁龙(哥伦布)寻找到东方大地(实际是美洲,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墨瓦兰(麦哲伦)由东洋(实际是美洲)到达中国大陆(实际是亚细亚的马鲁古),绕地球一周(卷四“墨瓦蜡尼加总说”)等。了解到麦哲伦环球一周的事实,则“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
李瀷根据子思的话,否定了“天地载水而浮”(张衡《浑天仪》)的传统浑天说/天圆地方说,由此展开论述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但是,李瀷的理论也有含糊之处。因为如果反过来看李瀷的说明,也许以下的说法反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即以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为依据,来揭示《中庸》第26章中的一句话里所隐含的意思,以此否定了传统的浑天说/天圆地方说。《中庸》第26章的这句话只是说“地振河海而不泄”,然而根据李瀷的观点,所谓“地振河海而不泄”就是指“地圆”,这一理论相比“天行健”即“天动”的说法,更是一种强辩而已。
(3)西学优越说
李瀷在进行东西科学理论比较研究之际,虽以实现两者的无矛盾统一、以经学理论为优的融合/折中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并没有将儒学/朱子学作为审视标准而让其发挥强烈作用。当他面对异端的西欧科学理论的绝对优越性之际,他承认传统科学存在缺陷,并向本国的知识人简要说明了西欧科学的内容及其先进性。例如阐释日月蚀发生原因的《日月蚀辨》以及说明东西岁差、南北岁差的《跋天问略》等便是此类著作。
李瀷特别赞赏传到东方的欧洲星历象数之学,主张西欧科学确实优于东亚的传统科学。例如除《日月蚀辨》《跋天问略》等以外,他在《星湖僿说·天地门》的《中西历三元》中指出:“西国之历,中国殆不及也。泰西为最,回回次之。”同样,在《历象》中,他也指出:“今行时宪历,即西洋人汤若望所造。于是乎,历道之极矣。日月交蚀,未有差谬。圣人复生,必从之矣。”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他的西学优越说。另外,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言西学的优越性,但是以其优越性为前提的论述其实也非常多。例如《北极高下说》《论周礼土圭》《地毬》等都是如此。
从西学优越说的立场来看,笼统、含糊地主张东西一致,其实这种主张无非是一方面承认西学的相对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儒学/朱子学当中也有类似之说。在李瀷的科学论当中,西学优越性是默认的逻辑前提,而以李瀷为代表的东亚西学研究者的中西会通论则应理解为这样的理念或思想潮流的结果,即18世纪以来显著的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宏观宇宙论乃至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结果。
二、洪大容的学术
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祖籍为京畿道南阳,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实学家。[18]
(一)燕行与思想革命
洪大容生于朝鲜朝英祖七年(1731),比李瀷大约晚50年。两人不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环境,甚至教育环境都不相同。与李瀷出身南人名门不同,洪大容出身老论世家。另外,洪大容于英祖十八年(1742),有志于“古六艺之学”,列入栗谷李珥→沙溪金长生(1548~1631)→尤庵宋时烈一系的金元行(1702~1772)之门下,属于朝鲜朱子学两大学派——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中的栗谷学派,这意味着他是以李珥为楷模来从事朱子学研究的。
洪大容自英祖三十五年(1759)到三十八年(1762)左右,制作了浑天仪。英祖四十一年(1765),随冬至使节赴中国清朝的京师(燕都)。第二年,访南天主堂,与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会谈,还与杭州读书人严诚、潘庭筠、陆飞进行了学术交流。回国后,提出“应向中国(从北方)学习”(北学)的主张,朴趾源等人也表示认同。英祖五十年(1774),荫补为世孙翊卫司侍直官。后历任泰仁县监、永州郡守等职。正祖七年(1783)去世,享年53岁。
1.洪大容与朱子学
洪大容的实学思想即燕行后的思想,看上去是与朝鲜两班思想不同的价值相对主义,富有批判精神,较诸李瀷更进一步地摆脱了朱子学的束缚,从其规范当中释放出来而获得了自由。但是燕行前,洪大容则完全固执于看似老论领袖宋时烈等人之说的以朱子学为独尊的立场。
例如,根据《湛轩集》外集卷三《乾净衕笔谈》1766年2月23日的记载,洪大容面对王阳明同乡的中国知识人,断然指出:
愚未见陆集,未知其学之浅深,不敢妄论。惟朱子之学,则窃以为中正无偏,真是孔孟正脉。子静如真有差异,则后学之公论,无怪其摈斥。
可见,他对于陆学及阳明学等所采取的似乎不屑一顾的态度。
但是燕行之后,这种孤陋的想法变得隐晦起来。根据《湛轩集》内集卷二《桂坊日记》1775年2月18日的记载,东宫(后来的正祖)对于洪大容思想中不受学统之局限的富有弹性的理气之解表示了赞赏:
桂坊(洪大容)之言甚确,观此言则桂坊似不为固滞之论。[19]这表明洪大容在经历了燕行之后,其思想信念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思想革命
洪大容燕行前后思想信念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要指出其变化的具体内容则并不容易。因此,本文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诗经·小序》与朱子《诗集传》解释的关系,看一看经过与杭州读书人的讨论,洪大容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1
以下的分析意在表明,通过与思想信念不同的浙人笔谈,洪大容对于构成自己思想基础的朱子学产生了一些怀疑。
根据《湛轩集》外集卷二和卷三《乾净衕笔谈》的记载,洪大容与浙人围绕朱子《诗集传》究竟应如何评价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始见于2月8日严诚(字力闇)的记录:
力闇曰:“朱子好背小序。今观小序甚是可遵,故学者不能无疑于朱子。本朝朱竹坨著《经义考》二百卷,亦辟朱子之非是,而自来之论,亦谓朱子好改小序,殆出于门人之手。”
严诚吸收了当时清朝知识人的朱子学批判,主张应当重视《诗经·小序》(诗序),并批评朱子在编撰《诗集传》(修订本,即今本)时,取郑樵之说,以为《小序》为乱经之元凶而将其删除。这是对拘泥于《诗集传》的攻序派而进行的批判。
对此,洪大容于2月10日写了反驳严诚的书信(《与力闇书》):
其破小序拘系之见,因文顺理,活泼释去。……乃其深得乎诗人之意,发前人所未发也。……至若小序之说,则愚亦略见之矣。……全不成文理,此则朱子辨说备矣。盖其踏袭剽窃,强意立言,试依其言而读之,如嚼木头,全无余韵。其自欺而欺人也,亦太甚矣。……若以《集注》谓非朱子手笔而出于门人之手,则去朱子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先辈之世、讲明若烛照,虽为此说者,岂不知其为朱子亲迹,而特以举世尊之,强弱不敌,乃游辞伪尊,软地插木,为阳扶阴抑之术也。
不过,严诚回应2月10日的《与力闇书》是在2月23日。严诚对于洪大容的反驳,仅冷淡地吐露一句:‘《小序》决不可废,朱子于诗注实多蹈驳,不敢从同也。”而且潘庭筠也站在严诚一边,指出:“朱子废《小序》,多本郑渔仲。”此外,陆飞也指出:“老弟宗朱,极是。然废《小序》,必不能强解也。”并在介绍马端临的说法之同时,指出朱子《诗集传》的不足,而且做出如下结论:“鄙意朱子注书甚多,或不无门人手作。”三人的主张都是基于当时新兴的清朝考据学的成果,并无丝毫过激之处,然而洪大容却回应道:“此不可以口舌争。请归而详览诸教。或有妄见,当以奉复也。”表示无法认同这样的主张。
到了2月26日,洪大容用预先准备好的文章来展开自己的观点,不过跟以前的一样,他反复强调:“诗之扫去《小序》,为其最得意处,而大有功于圣门矣。及闻兄辈之论,不觉爽然,而自失矣。”严诚等三人对洪大容的反驳又进行了再反驳,据说是“酬酢颇多”。
但是,论战的结果却是洪大容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失败,向三人表示了自己内心想法的变化:
东国知止有朱注,未知其他。弟之所陈,亦岂敢自以为不易之论耶。至于小序,一读而弃之,不复精究。当于归后,更熟看之。
据《乾净衕笔谈》的记录,论战获得圆满结束,据称“诸人皆有喜色”。
洪大容通过与中国清朝知识人的笔谈,接触到新学问的一角,引发了自己的思想革命,开始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作为自己思想基础的朱子学,尽管只是局部的批判。
这类批判在《毉山问答》一书中有显著的表现。虽然他还奉行老论一系的朱子学,然而另一方面他对朱子学末流之弊表明了对决的姿态,并企图加以改革,此即燕行后洪大容的思想立场。这也就是为何在他的思想主张中,并没有朱子学者常见的那种道学式的固执与独断的毛病。
换言之,持价值相对主义立场的洪大容的思想就是在信奉朱子(宗朱)与批判朱子(攻朱)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基础上而得以成立的。
(二)基本思想
洪大容的基本思想即燕行后的思想与李瀷相同,其特征是在宗朱与攻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若对其思想特征进行归纳的话,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批判形式化、空洞化的朝鲜朱子学,立足于朝鲜的现实,主张实用的实际学问(实学)的必要性;
第二,支持中国清朝的善邻对外开放政策,主张必须积极地吸收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北学);
第三,提出“以天视物”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
1.实学
不过,上列第一的“实学”观,很有可能是受其恩师金元行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是因为根据《湛轩集》内集卷四《祭渼湖金先生文》(1772)的记载,洪大容曾经得到金元行的如下教诲:
问学在实心,施为在实事,以实心做实事,过可寡而业可成。
另外,《湛轩集》外集卷一《答朱郎斋文藻书》(1779)中则提到:
吾儒实学,自来如此。若必开门授徒,排辟异己,阴逞胜心,傲然有惟我独存之意者,近世道学矩度,诚甚可厌。惟其实心实事日踏实地。先有此真实本领,然后凡主敬致知修己治人之术,方有所措置,而不归于虚影。
可见,洪大容的实学观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为了追求真正的朱子学。
2.北学
上列第二的“北学”即主张必须积极地学习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重视清朝文化。洪大容通过自身的燕行经历,将此主张付诸实践。从其实践的事实来看,或许与其个人的资质有很大的关联。例如洪大容学习并掌握了中国语(北京话)的会话,尽管可能并非十分熟练;另外,他与那些从朱子学(名分论)的立场出发而对辫发感到羞耻的汉族知识人也有深入的交流。洪大容所追求的与异民族的宽和交往,其结果正呼应了中国清朝的善邻对外开放政策。批判了基于朝鲜朝老论的朱子学(华夷论)的非现实的清朝敌视政策(北伐论),这就意味着宋时烈所提倡的孤陋狭隘的自尊自大之政策的失败。归国以后,老论主流派的北伐论者(金钟厚等)批评洪大容与清人的交往乃是违反了朱子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交友方式,若从当时两国外交的形势来看,这类批评可以说是必然的反应。
3.以天视物
关于第三点,即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毉山问答》与《林下经纶》当中。其中,洪大容阐发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毉山问答》)
主张人类中心的价值观是不足取的,而构成其“人物均论”的基础则无非是“以天视物”这一观点。所谓人物均论,与其所属的老论、洛论的人物性同论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且不论他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正如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他的人物均论确是受到了人物性同论的影响。
此外,洪大容并没有将“以天视物”设定为人与禽兽草木的本质差别,而是将其价值相对主义观点应用于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理论,其因在于他拥有“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的观点。他的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
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诸侯衰弱,吴楚滑夏,寇贼无厌。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这是主张从华夷论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批判歧视异民族,此即所谓“域外春秋说”。此外,洪大容由这样的观点出发,梦想建立基于能力而没有身份制的万民皆劳的社会(《林下经纶》)。
(三)价值相对主义与西学知识
燕行后的洪大容,就生活在思想与现实或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矛盾纠结中,并在趋向不同的两种张力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可以推断此即洪大容价值相对主义得以形成的缘由。不过,《毉山问答》一书所披露的价值相对主义,并不是消极的、脆弱的,而是充满着倡导实学以及全面否定虚学的毫不动摇的自信。其充满自信的原因在于,他的思想主张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
1.地球说与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
据洪大容的《毉山问答》,若要问人类社会之当为与价值相对主义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何在,则无外乎起源于欧洲的科学知识[21],即地圆说与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这是因为“人物之生,本于天地。”
洪大容认为大地是由球形构成的:
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
另外,他以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为依据,指出:
满天星宿,无非界也。自星界观之,地界亦星也。无量之界,散处空界。惟此地界,巧居正中,无有是理。
这是说,不能将地球看作宇宙的中心(“空界之正中”)。
2.价值相对的社会理想与天地的相对性
洪大容利用西欧的科学知识,揭示了天地的相对性,进而提到了“人物之本”“古今之变”“华夷之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地球也非宇宙的中心。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必要以中华为贵,也没有必要遵从华夷秩序。
毫无疑问,洪大容坚信本国未来遥远的前途、提倡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理想,他的这种心情定能超越时代传达给读者。价值的相对化是必然的。
若对以上所述用命题化的方式做一归纳,那么可以这样说,诱发出洪大容的价值相对主义社会思想,是由于跟中国知识人的真心交流,但是其理论支撑则是传播到东亚的崭新的欧洲数理科学知识。
三、小结
李瀷与洪大容,将倭乱、胡乱之后出现的朱子学相对化推向极致,是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实学家。可以说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将朱子学与西学二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若要对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想的展开做一推断,无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朝鲜实学不仅与朱子学的学统相关,而且他们个人也是发自内心地尊敬朱子的学德,并以李滉或李珥为楷模,来从事朱子学研究。与此同时,又受到朱子学改革主义的影响,或者因燕行而发生思想革命,导致他们开始对朱子学作一番相对化的尝试。而引发相对化的无疑是理义。在尹东奎所撰的《星湖行状》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瀷)如其义安则不规规于人己,理得则不切切于毁誉。勇往直前,不顾傍人是非。”这个说法生动地描绘出李瀷等实学家重视理义的研究态度。无疑,实学家一方面要注意不能大幅度地越出朱子学的架构,另一方面又乐于追随理义而自由地思索。
其次,在追求理义的过程中,他们与西学相遇,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实学的视野。与擅长实用与逻辑的西欧科学的邂逅,其影响尤其之大。实学家经历了由西学东渐而导致的18世纪东亚的宏观宇宙论(cosmology)的转换(变化),并受到西学魅力的影响而开始了真正的西学研究。在西学当中,西欧科学之实用性且又精致的理论,使得这些实学家自觉到自己视野的狭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刺激。通过热心地研究西学,其结果使得实学家步入了新的学问路径以及新的知识世界。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异端持宽容态度的反朱子学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异端,只要其中有可学习之处,便应毫不犹豫地加以学习;也是强调中西会通,即强调经学理论为优的朱子学与实学以及西学之间的理论整合与折中。实学家在西欧科学由微至细的学习(刺激)之下,对传统学风进行修正,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学问构架。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作者单位:日本东京大学,译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校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李甦平
李退溪(1501~1570)是韩国朝鲜朝时代一位继往开来,有创造性的重要儒者。他“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1]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关于理气的问题,他更加强调的是“理”的重要性和活动因素;关于心性情的问题,他突出了从“情”的视角对“四端”和“七情”的研究;关于践履问题,他竭力主张“敬”是成圣的须臾不可离的工夫。
一、“理”论
作为一名性理学者,李退溪用“理气”范畴来说明、解释宇宙、人生、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关于“理”,退溪认为“理”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又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正是由于它既重要,又难理解,古今学者对它进行不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李退溪的这一分析、判断是很准确的,不论是韩国性理学,还是中国理学,其学派分殊,大都源于对“理”的理解的差异。那么,李退溪是如何理解“理”的?他关于“理”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笔者认为,李退溪“理”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强调理气不杂。李退溪思想中的“理”以“极”的意义为其前提。如当学生问“理字之义”时,他回答说:
若从先儒造舟行水,造车行路之说仔细思量,则余皆可推也夫舟当行水,车当行路,此理也。舟而行路,车而行水,则非其理也君当仁,臣当敬,父当慈,子当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则非其理也。凡天下所当行者,理也。所不当行者,非理也。以此而推之,则理之实处可知也。
又说:
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放之无外者,此理也;敛之无内者,亦此理也;无方所、无形体,随处充足,各具一极,未见有久剩处。[2]
李退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船在水中行,车在陆上走,这是船、车之理。反之则不是船、车之理。同样,国君仁,臣子敬,父亲慈,儿子孝,这是君臣父子之理。反之则不是君臣父子之理。所以,理不分大小,没有哪样事物能超越理,也没有哪样事物不被理所包含。这说明,理没有空间,没有形体,随时随地都是完美的,它是事物的极至。“各具一极”的“极”,除了“极至”的意思之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如李退溪在《答南时甫(乙丑)》中说:极为之义,非但极至之谓,需兼标准之义,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看,方恰尽无遗意耳![3“极”除了“至极”“极至”的意义外,还具有“标准”的意思。因此,理是事物的标准。这是说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其事物,是由于理这一基准的作用或规定。理既具有极至、至极之义,又兼有标准、基准之义。这样的理,其特性是“形而上”。李退溪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形而下者,而其所具之理都是形而上者。
在性理学中,与“理”相对的概念是“气”。关于“气”,李退溪认为主要指阴阳五行之气,即“二五之气”。李退溪依据朱熹的“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来”和“阴阳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的思想,认为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变化而化生万事万物。
李退溪认为阴阳二气能够生成具有形象的万事万物,故“气”又是形而下之器,具有“形而下”的特性。
固然,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李退溪依据朱熹思想,也看到了“理”与“气”相须不分的关系。如他说:“天下无无理之气,无无气之理”。[4]他承认“理”与“气”相依不离的关系。但为了批评中国明代罗钦顺和韩国朝鲜朝徐花潭的主气观点,他认为更应强调的是“理”与“气”相分不杂的关系。
关于理气不杂的关系,李退溪指出“理”为道、为贵、为善、为形而上,“气”为器、为贱、为恶、为形而下。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然”与“所以然”的关系。
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5]
其飞其跃固是气也,而所以飞,所以跃者,乃是理也。[6]李退溪认为理气相杂的关系可以以“帅”和“卒”比喻。“理”为主导、为统帅,“气”为非主导、为兵卒。“理”与“气”有这种分殊,是因为“气”是“然”,即飞和跃是“气”的运动或发,而“气”之所以能够那样,是由于“理”的“使然”,即由于“理”统帅的结果。李退溪认为“理”与“气”的这重关系被主气学者所忽视,过于偏袒理气不分而导致认理为气或提倡理气非异物说。“近世罗整庵倡为理气非异物之说,至以朱子说为非是”。[7]
李退溪指出,朱熹在《答刘叔文书》中对“理”与“气”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辩证论述并明确指出:“理与气决是二物”。但主气论者徐花潭却“终见得理字不透”,总在“气”上下工夫,最终成为朱熹所批评的“气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气为性之误”那样的人。可见,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方面,主张理有动静。如果说强调“理气不杂”是李退溪理思想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第二个特点则是主张“理有动静”。
关于“理”有无动静的问题,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主张太极(理)自身并不动静,只是所乘之机有动静。如果说到太极动静,也只是指理随气而动,朱熹讲的“天理流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并不是指理在气中运动或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理的世界在运动。这一思想朱熹后来做了进一步发展,如《语类》记载:“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卷九十四,周谟录)这是说周敦颐所谓阳动阴静并不是指太极自身能动静,所以说“非太极动静”,动静的主体是阴阳,动静的根据是理。能够运动的二气与自身不动的太极好像人跨马行走,人(太极)没有绝对运动,但有相对运动。
上述朱熹所谓的“理有动静”有两个意义。其一指理是气之动静的根据。朱熹在答郑可学书云:“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或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文集》五十六,《答郑子上》)这是说气的动静是以静之理动之理为根据的。朱熹答陈淳之问说:“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语类》九十四,陈淳录)气之动乃为其中有所以动之理为根据使然,气之静乃为其中有所以静之理为根据使然。其二,从理一看,实际只是一个理;而从分殊看,用处不同,或为动之理,或为静之理,故亦可说理有动静。综上所述,从本体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8]如朱熹曾明确地说过:“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9]明代学者薛瑄修正朱熹的“理不可以动静言”的观点,认为理自会动静。如“又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10]这是说,理(太极)既不自会动,便是死理、死人;既是死理、死人,便不能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既不足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之原”,便不能为气(阴阳)动静的根据,气(阴阳)亦不以死理(太极)为动因。这样,理何足尚,人何足贵!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承认理(太极)自会动静,理(太极)不需乘气(阴阳),气(阴阳)不需以理(太极)为动因,理气一体,理与动静一体才可。这就意味着理自会动静。
李退溪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太极生阴阳,理生气的问题,同时避免朱熹在理能否动静问题上的模糊性,他接受了薛瑄等人的太极(理)自会动静说,明确提出理有动静。如当李公浩以朱熹的理无情意、无造作,恐不能生阴阳相问时,他回答说:
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
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11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引朱熹那段话的旨趣,与朱子以形而上之理(太极)是形而下之气所以动静的根据但理自身不动的思想相符合。而李退溪却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个意义上引用朱熹的话,这就与朱熹思想稍有差异。而这个差异正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发展。[2]李退溪在《答郑子中别纸》中还讲到了理自会动静的思想。如:“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13] 这里,李退溪指出,由于理动才会生出阴阳之气。他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时,也明确指出,周敦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自会动静。正是由于理的动静,才有阴阳之气的产生。主张“理自会动静”,这是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而李退溪提出的关于“四端”“七情”的理气互发说,也正是在理自会动静这一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情”论
李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在韩国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这是因为退溪提出的“四端七情”论导致了近代朝鲜朝儒学界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形成和对立。围绕四七论而形成的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对立,堪称朝鲜朝性理学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构成了“儒学的韩国化”。这就是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论成为韩国性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探究退溪的四端七情论具有探究儒学韩国化的典型意义。
四端七情论中的“四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七情论中的“七情”,指《礼记》中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李退溪关于“四端七情”的原创性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四端”与“七情”的区别,认为“四端”与“七情”属于两个不同质的“情”范畴。二是用“理气观”对“四端七情”加以诠释。“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14]李退溪认为关于性情问题,先儒已经论述得很周详了。但是,用“理”和“气”来分析、阐释四端与七情,先儒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所以,以“理气”观解释“四端七情”,这确是李退溪的一个贡献。
如上所述,李退溪“理气”观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二分说,即突出理气不相杂的一面。循着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四端七情”问题上,他仍然主张“四端”与“七情”的相别和相殊,即强调“四端”与“七情”的不同质。
李退溪认为情之所以有四端和七情之分,就犹如性之有“本性”与“气禀”相异一样。而性,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为什么情就不可以用理、气分别言说呢?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从仁义礼智的性中发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呢?是外物与身体接触而引起心中的感动,即源于外界事物而发。四端的发出,孟子说是心,而心是理与气之合,然而为什么所指是理?仁义礼智之性猝然在心中,而四者是其端绪。七情的发出,朱子说是“本来就有的当然法则”,所以并不是没有理。然而为什么所指是气?外物的到来,最易感觉并先动的,也就是形气了,而七者是其苗脉。哪有在心中是纯理,而才发出就为杂气了呢?哪有外感是形气,而能为理本体发出的呢?
可见,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所指”。李退溪认为“四端”的“所指”是“理”,“七情”的“所指”是“气”。他的这一思想在《论四端七情第二书》中讲得更明确,如他说:“若以七情对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于气犹四端之于理也。其发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15]“七情”为“气”,“四端”为“理”。这就是四七的“所指”。而在李退溪的思想中,“理”与“气”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理”指事物的法则、本质,“气”指事物的质料(材料)。不仅如此,其性质也不同。“理”是形而上的,具有抽象、普遍的性质;“气”是形而下的,具有具体、特殊的性质。进而,李退溪将其分属于“四端”和“七情”。这就决定了“四端”与“七情”的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是其价值的区别,即“四端,皆善也。……七情,善恶未定也。”[16]他根据孟子思想,认为“四端纯善”是绝对的。由此可见,四端是抽象的情。另一方面,他讲情,并非是作为理想的、完人的圣人之情,也有常人之情,即具体的情。这样,他的四端七情就具有了互相不同的意义和特征。[17]为了进一步论证“四端”与“七情”的不同,退溪在上述引文中提到“其发各有血脉”。所谓“其发各有血脉”,也就是“所从来”的问题。
李退溪在《答奇明彦第二书》中说:“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耳。”[18]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解读李退溪的这一思想:
第一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四端可谓理之发,但此时并非无气,而气的作用是顺理(随之)而为。七情可谓气之发,但并非唯气之发,此时亦有理(乘之)。”这样解释,主要是为了回答奇高峰的诘难。奇高峰主张,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应从“理气不相离”的“浑沦而言”的角度解释。所以,李退溪在说“理之发”“气之发”的同时,又补充上“气随之”“理乘之”,以表明“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而实质上,退溪的意思还是强调“四端”为理发,“七情”为气发。他所谓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的意思,就是“理之发,气之发”。正是由于“四端”是“理之发”,所以“自纯善无恶”,只有当“理发未遂而揜于气”时,才会流为不善。正是由于“七情”是“气之发”,所以当“气发不中而灭其理”时,就为“放而为恶”。在这里,可以从李退溪的理气不离的论述中,窥见他实质上还是从理气相分的角度来阐释“四端”与“七情”形成的根源。
第二点,李退溪所说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中的“发”“随”“乘”是三个关键性的动词。
“发”,是活动的意思。“气发”,即指气的活动,气是可以动的。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理发”,应解释为理的活动。如上所述,朱熹不承认理有动静,所以他说的“四端是理之发”为“虚发”。而李退溪对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认为理有动静。这样,在退溪的理论系统中,不论是“四端理之发”,还是“四端,理发而气随之”的“发”,都是讲的“实发”,即“理发”与“气发”的“发”,是一个意思。正是基于承认理有动静的观点,退溪竭力主张四端是理发。
“随”,是跟随、尾随,即随着的意思。李退溪讲“理发气随”,就是表明气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理发气随”的“四端”,是纯善无恶的。
“乘”,是坐、驾的意思,所以“气发理乘”就是讲,气发而理驾驭气。当气发,而理能驾驭气时,七情表现为善;当气强理弱,理驾驭不了气时,七情易流于恶。
李退溪通过“发”“随”“乘”三个关键动词,凸显了“理”的活动性、主宰性,即表明了他对“理”价值的肯定。
第三点,李退溪讲四端为理之发,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性善”说。孟子从“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表露现象推测到仁义礼智之性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从四端皆性的意义上讲四端的“本旨”即意图。所以,李退溪讲“四端自纯善无恶”,是“理之发”,正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之上。性善说的立场作为退溪学问的立场,是先行于其方法论的前提。19
三、敬论
“敬”是理学家成圣修养的重要工夫之一,作为性理学者的李退溪固然知道这一道理。为此,退溪把“敬”作为自己学问的重要内容。《圣学十图》是退溪晚年的经典之作,可视为他学问体系的全部内容。而退溪却以“敬”之一字评价他《圣学十图》的基本内容:“今兹十图,皆以敬为主焉”。20这就是说,敬彻上彻下,贯通十图之间
李退溪的主敬思想是其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如上所述,在理气观上退溪重理轻气,视理善气恶,由此导致在性情观上,他主张“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宰之”,这就是说“四端”理发为善,而“七情”气发为恶;这就必然得出“四端,道心是也”“七情,人欲是也”的结论,进而“道心”又可称为“天理”,而“人心”则是“人欲”。要想“遏人欲,存天理”,最重要的修养工夫便是“敬”。“敬以直内为初学之急务”,“敬以直内为日用第一义”,这是说“敬”是涵养大理,遏去人欲的根本方法。
李退溪关于“敬”的理论与朱熹“居敬”“主敬”的学说,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即强调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但李退溪超过朱熹的地方是在实践、践履“敬”的真功实行方面。
本来,个人修身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始终是理学的基点和归宿。可是,在程颐,特别是在朱熹哲学中,由于更多地容纳了追求外界知识的内容,造成了格物穷理的具体活动与理学所规定给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之间的某种不一致。……因此,在格物穷理上包含着可能突破理学的倾向:一种是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的修养;一种是完全投入自然事物的研究。21可以说,日本朱子学是在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上,发展了中国朱子学而走上了一条以追求客观经验之理为目标的道路。22I而李退溪的“敬”的实践主张则是对埋头古人之书而忽略身心修养弊病的一种突破,亦是对恢复孔孟修身养性成圣传统思想的努力实践:
李退溪之所以强调突出“敬”的实践工夫,也是由朝鲜朝社会自身内部原因所决定的朝鲜朝时期“士祸”迭起,许多知识人惨遭杀害。从燕山君至明君(1495~1545)短短的五十年间,就发生了四次大士祸,被残害的读书人多达一百八十余人。李退溪的岳父权〓的父亲权柱就在“甲子士祸”(1504)中被处死,权〓遭株连被流放到济州岛,李退溪本人也受到株连,被剥夺了授予的春秋馆记事官职位。李退溪亲历了四次“士呙”,口睹了亲朋好友及学者文人的悲惨遭遇,认为惩治这一弊端的措施就是去恶从善以治心,故立志“敦圣学以立治本”。而“治本”“治心”的关键就是“敬”的修养工夫。
李退溪强调“敬”的实践工:夫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圣学十图》之中。《圣学十图》中十个图就有四个图是谈“敬”的修养工夫这就是:
《第三小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写道:“吾闻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23]李退溪认为“敬”的工夫贯彻圣学之始终,所以,《小学》所谓的洒扫、应对进退的仪表、节度等内容就是“敬”的工夫。这些关于“敬”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大学》的明德、新民之功。
《第四大学图》,李退溪在此图后也做了一段说明:
然非但二说当通看,并与上下八图,皆当通此二图而看。盖上二图是求端扩充,体天尽道极致之处,为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下六图是明善成身,崇德广业用力之处,为小学大学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彻上彻下著工收效,皆当从事而勿失者也。24
这里的“非但二说”,即指小学图和大学中所引朱子关于“敬”的论说。李退溪的意思是说,从本质上二看,《圣学十图》讲的都是关于“敬”的道理。《第一太极图》和《第二西铭图》讲的是“立太极”和“立人极”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主“敬”的问题,故李退溪说是“小学大学之标准本原”问题。而《第五白鹿洞规图》《第八心学图》《第七仁说图》《第八心学图》讲的是如何明善、如何诚身、如何盛德等身心修养问题。而这些身心修养问题,关键处是“要之,用工之要,俱不离乎一敬。盖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25]所以,《大学罔》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事功,都离不开敬。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也是“敬”的实践过程。
《第九敬斋箴图》告诉人们“敬”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如何行为才能做到“敬”。李退溪认为持敬就是主体心的“主一无适”。从持敬的静弗违来说,便是正其衣冠,尊其赡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从动弗违来说,便是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这就构成了动静弗违。弗违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被动接受。从持敬表交正而言,便是出门如实,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从持敬裹交正而言,便是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这就构成了表裹交正。交正是主体心(人)对于客体敬的主动适应。虽然心有间、有差,但只要心敬,依照动静弗违,表裹交正的规定来体玩警醒,日用实践,就能消除有间和有差。
《第十夙兴夜寐箴图》旨在表明敬在人们行为上如何贯彻。第九图和第十图都是讲持敬行为,但二图也有不同。不同之一是第九图“有许多用工地头,故随其地头而排列”;第十图“有许多用工时分,故随其时分而排列”。[26]这就是说,第九图是按事件而讲敬的修持工夫,而第十图是按时间而讲敬的要求训练。不同之二是第九图以“心”为核心而展开敬的工夫;而第十图则以“敬”为核心而辐射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情感。例如早晨醒来的思虑情感,省旧紬新和早晨起来的行为践履,虚明静一,然后读书应事,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从鸡鸣而寤,到昧爽乃兴,从读书对越圣贤到应事则验于为,再从日间动静循环,休养性情到晚上日暮人倦,心神归宿,都做了仔细的规定。
第九图和第十图两图结合,便明确了何时、何地、怎样做才是持敬工夫,才能做到无毫厘之差,由此,也才能达到“作圣”的境界。[27]
可见,主张持敬的实践工夫是李退溪性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他以成圣为性理学的目标,而成圣的关键是通过“敬”的修养工夫,明善诚身以至为仁、为圣,这是李退溪的终极关怀。
(原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
⊙李存山
在宋代理学的“濂洛关闽”谱系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占有开山的地位,其对于朱子理学之思想体系的形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太极图说》开山地位的确立,却是经过一个历史过程的。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对这一过程的论述。
一、关于《太极图说》的争议
《太极图说》有图有说,而其图其说在理学发展史上都有争议。
首先,关于周敦颐所传“太极图”,主要是其来历的争议。南宋初,朱震(字子发)在《汉上易传表》中说:“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此后,陆九渊与朱熹辩“无极”与“太极”,指出:“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修),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抟),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至明清时期,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详加考辨,认为周敦颐所传“太极图”出自道教的《上方大洞真玄妙精品》中的“太极先天之图”或陈抟所传的“无极图”。近现代学者多有从其说者。
然而,朱熹在《太极通书后序》中说:太极图乃“(濂溪)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其根据是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所记:“(濂溪)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今人或谓“太极图易说”即是《太极图说》,但朱子在序中说“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可知朱子是把“太极图、易说、易通”理解为三本书。)
对于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认为“太极图”乃出自道教“太极先天之图”或“无极图”的考辨,今学者李申在《话说太极图》中予以否定,其根据是王卡在《道藏提要》中指出:道教的《上方大洞真玄妙精品》及《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并非唐代作品,其中提到的“真武真君”是宋真宗时所立,且其中引用了“山谷曰”(山谷即黄庭坚,与周敦颐同时),据此可证道教的“太极先天之图”当出自周敦颐所传“太极图”之后。至于黄宗炎在考辨中提到的“无极图”出于河上公、后来陈抟将之刻于华山石壁,李申也指出此说在黄宗炎之前没人说过,近于神话,并不可信。[1]
在李申提出上说之后,又有束景南、姜广辉、陈寒鸣、张其成等学者提出商榷。[2]关于“太极图”来历的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其次,关于《太极图说》的“说”,其首句除了“无极而太极”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版本,一是国史本作“自无极而为太极”,二是九江本作“无极而生太极”。朱熹把“无极而太极”解释为“无形而有理”,陆九渊则认为“无极”之说出自老子,而圣人只言“太极”,不言“无极”,《太极图说》在“太极”之上又言“无极”,是蔽于老子“有生于无”之说。朱、陆的“无极”与“太极”之辩,双方都持论甚坚,往复辩论,最后是以朱熹提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无复可望于必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六》)而告终。
对于以上争议,现代学者评价不一。笔者认为,自先秦以来儒家与道家都有“气(阴阳)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思想,秦以后儒、道两家亦共用“气(阴阳)—天地—(阴阳)五行—万物”的模式,这是儒、道两家共有的本体—宇宙论架构。两家所不同者,是道家、道教在“元气”之前还有“道生一”或“无生有”。而儒家对于这一不同的理论自觉,始于宋代的张载,即所谓“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正蒙·太和》),“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正蒙·大易》)。但是在张载之前,儒家尚未达到这种理论自觉,或者说并未将此看得有多么严重。如《易纬·乾凿度》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但其又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说,所谓“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郑玄注:“太易,无也;太极,有也。”《乾凿度》和郑玄虽然采用了道家的“无生有”之说,但其讲“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故其仍属于儒家。从儒、道两家都有“阴阳五行”的本体—宇宙论架构,而其区别主要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作为宋代理学之开山的周敦颐《太极图说》,确实在理学的思想体系建构中具有开创的地位。而辨别“太极图”的来源以及“无极”与“太极”的关系,则是后人用张载、二程以后的观点来求全于周敦颐,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释亦是以后人所求之全或他所理解的二程理本论来创造性地诠释《太极图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认为“周子《太极图说》本‘易有太极’一语,特以‘无极’二字启朱陆之争”,毛奇龄考证此图的来源以及“无极”等语不是儒书所有,其立议“不为无因”。“惟是一元化为二气,二气分为五行,而万物生息于其间,此理终古不易。儒与道共此天地,则所言之天地,儒不能异于道,道亦不能异于儒。”就此而言,毛奇龄“不论所言之是非,而但于图绘字句辨其原出于道家,所谓舍本而争末者也”。《四库》馆臣的这一评论是有见地而中肯的。本来儒、道两家共有“阴阳五行”的本体—宇宙论架构,儒家要“推天道以明人事”也不能舍此架构而不用。如果不论周敦颐在用此架构时的价值取向如何,而只是辨此图“原出于道家”,那就是“舍本而争末”。
《太极图说》讲“无极而太极”,又讲“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这里应有道家、道教的思想因素(周敦颐也确曾受到道教的影响,其诗有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几”,见《周子全书》卷十七),而周敦颐当时并不以此辨别儒、道,也就是并不将此看得有多么严重。关键是道教用“无极图”或“太极图”来讲“逆则成丹”,而周敦颐则用此图式来讲“顺而生人”,从“天道”推衍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儒家价值取向(所谓“立人极”即确立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此而言,《太极图说》在宋代理学中确实具有开创地位。
二、二程为什么不传《太极图说》
程颢、程颐早年曾受学于周敦颐,但是周、程的师生关系是常被议论的话题,而且二程不传《太极图说》,其原因更值得探讨。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近)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程氏文集》卷十一)
这段记载就隐含着周、程之关系的复杂性。“周茂叔论道”,其所论之“道”是否就是二程所创理学的“道”,二程似没有给予肯定。二程闻“周茂叔论道”的结果是“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但“未知其要”,这似可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周敦颐的“论道”还没有达其“要”;另一种是二程所学还没有达周敦颐的“论道”之“要”。从后面所说二程“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近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看,所谓“未知其要”应做前一种理解,即周敦颐的“论道”还没有“臻斯理”,而二程的理学是自得于六经,为秦汉以下所未有。这符合程颢所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氏外书》卷十二),也符合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所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氏文集》卷十一)。
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程氏遗书》卷三)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也说:程颐“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程氏遗书》附录)这里的一个细节是,二程往往称周敦颐为“周茂叔”,而不称“先生”(程颐对于胡瑗则“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朱熹则在“周茂叔”之后加上了“先生”二字。
二程从周敦颐处所得最受用的就是“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有‘吾与点也’之意”。这种境界就是儒家的以“道”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超越了自身功利的境界。有了此境界,二程“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在周敦颐的教导下,二程有了此境界,以后“孔颜乐处”“吾与点也”遂也成为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仅此一点,周敦颐是否就成为理学之开山呢?其实不然,因为宋儒讲“孔颜乐处”并不始于周敦颐,而是始于范仲淹。
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范仲淹就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锺君恨即销。”(《范文正公集》卷三)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亦教导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宋史·张载传》)。当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集·年谱》)“孔颜乐处”实即范仲淹所说的“道义之乐”,亦即儒家把“道义”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超越了对自身功利得失的计较。因为把“道义”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所以当有了“得道”之感时也就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3]
据《范文正公集·年谱》,范仲淹在景祐二年(1035)在苏州建郡学,聘请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景祐三年徙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此建郡学,“生徒浸盛”;景祐四年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在此建郡学;宝元元年(1038)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今江苏绍兴)。在这段经历中,范仲淹与为母守丧的周敦颐有一年多的时间同在润州,此期间周敦颐当受到范仲淹的影响。[4]而二程受学于周敦颐,则是在此后的庆历六年(1046)。
宋代新儒学的兴起似可分为两步:其一是儒家的价值取向的确立,此即范仲淹、周敦颐所讲的“孔颜乐处”等;其二是新儒家的“本体—宇宙论”思想体系的建构,此即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开其端。有了这第二步,周、张、二程等才成为“新儒中之新儒”。[5]
史料未载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于何时。可以肯定的是,在程颐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时,《太极图说》就已完成了。朱熹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氏遗书》附录)
这里的“皇祐二年”(1050)应为“嘉祐二年”(1057)之误[61。此时程颐二十五岁,写了长篇的《上仁宗皇帝书》,呼吁改革,表达了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内圣外王”的意识。因上此书后“不报”,程颐乃“闲游太学”,主持太学的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云:
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程氏文集》卷八)
这段话中的“天地储精”至“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是有取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此后的“其中动而七情出焉”至“故曰性其情”,则是程颐有取于胡瑗的《周易口义》。[7]
朱熹后来论及二程思想与《太极图说》的相承关系,他说:“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在朱熹举证的程氏三篇中,以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为最早。这三篇都只是节取了《太极图说》中“二五之精”以下的意思,而不讲“无极而太极……分阴分阳,两仪(天地)立焉”。《颜子所好何学论》从“天地储精”讲起,实已显露出二程之学的一个特点,即他们认为“学之道”就在既成的天地万物和人的现实世界中,这个世界虽然有“本”,但无须“穷高极远”地探讨天地之先的问题。
《程邵公墓志》是程颢在其次子去世的熙宁元年(1068)所写,有云:“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程氏文集》卷四)这里的“动静者阴阳之本”,显然也是要回避“无极”和“太极”之说。程颢的《李寺丞(仲通)墓志铭》作于熙宁七年(1074),有云:“二气交运兮,五行顺施;刚柔杂揉兮,美恶不齐;禀生之类兮,偏驳其宜;有钟粹美兮,会元之期。”(《程氏文集》卷四)这里也只言“二气”“五行”,而不言“无极”“太极”以及“是生两仪”。可见,朱熹所说“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实际上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的“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8]。这当是二程不传《太极图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熹说:“二程不言‘太极’者,用刘绚记程言,清虚一大,恐人别处走,今只说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所谓“刘绚记程言”,实为吕大临记程言,即《程氏遗书》卷二上记载二程所说:
横渠教人本只是谓世学胶固,故说一个清虚一大,只图得人稍损得没去就道理来,然而人又更别处走。今日且只道敬。
朱熹是把二程对张载之学的批评作为其不言“太极”的原因,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二程还曾说:
《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程氏遗书》卷二上)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同上)
二程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张载的《订顽》(即《西铭》),另一方面对张载超出《订顽》而讲“太虚即气”(“清虚一大”)等有所批评。张载的《订顽》讲“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在二程看来,已经表达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故云“意极完备”,“乃备言此体”,如果超出了《订顽》,那就是“恐于道无补”的“穷高极远”,“人又更别处走”。
值得注意的是,《订顽》从“乾称父,坤称母”讲起,这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不讲“无极而太极”,从“天地储精”讲起,是一致的。二程对张载之学的批评,可能也正是二程对《太极图说》的不满意之处。当然更可能反过来说,正因为二程对《太极图说》讲“无极而太极”不以为然,所以二程对张载讲“清虚一大”也有所批评。
二程不讲“无极而太极……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即对《易传·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也予以回避。但是二程对《系辞》中的“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以及“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则多所发挥[9],这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从“天地储精”讲起也是一致的。
二程不言“太极”的原因,也就是二程不传《太极图说》的原因。朱熹说:
《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及“东见录”中论横渠“清虚一大”之说,“使人向别处走,不若且只道敬”,则其微意亦可见矣。若《西铭》则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远,于学者之用为尤切,非若此书详于天而略于人,有不可以骤而语者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
朱熹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不得已而作”,此“不得已”意谓“道体”幽微难言而又不得不言。其实,二程之所以不传《太极图说》,并非弟子中“未有能受之者”,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二程主张“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若讲“天道”则从“天地设位”或“天地储精”讲起就可以了,而不必“穷高极远”地讲“无极而太极……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三、北宋以后周、张著作的流传
北宋以后,在朱熹的学术成长时期,二程洛学主要分流为由杨时所传的“道南学派”和由胡安国所传的“湖湘学派”。朱熹在十四五岁时就曾读二程和张载“两家之书”10],亦曾习禅学,自二十四岁后受教于杨时的二传李侗,“李先生极言其(禅学)不是”,乃专心读“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一〇四)。在师事李侗之前,朱熹亦曾师事胡宪(胡安国从子),故亦较早受到湖湘学派的影响。
杨时最初对张载的《西铭》提出批评,后得到程颐的纠正(参见《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除《西铭》外,杨时及其所传道南学派对张载的《正蒙》持排斥态度,而胡安国及其所传湖湘学派则肯定《正蒙》。朱熹在受教于李侗时,“尝看《正蒙》,李甚不许”,“李先生云:横渠说不须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费力”(《朱子语类》卷一〇三)。道南学派的这种态度,类似于二程从“先识仁”的角度批评张载之学。而湖湘学派则对濂学和关学都持开放态度,这与胡安国及其季子胡宏同程门弟子侯仲良有过密切的接触有关。
侯仲良,字师圣,《伊洛渊源录》谓其“河东人,二先生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皆出衡山胡氏”。又载其遗事,“或曰:江陵有侯师圣者,初从伊川,未悟,乃策杖访濂溪。濂溪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伊川亦讶其不凡,曰:‘非从濂溪来耶?’师圣后游荆门,胡文定留与为邻终焉。”朱熹辨别此遗事不实:“濂溪卒于熙宁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间尚在。其题上蔡谢公手帖,犹云显道虽与予为同门友,然视予为后生。则其年辈不与濂溪相接,明矣。”(《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朱熹此说可商榷,周敦颐卒于熙宁六年(1073),此距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有五十余年,若侯仲良在二十岁上下见晚年的周敦颐,不是不可能的。
《伊洛渊源录》又载胡安国的《与杨大谏书》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门溃卒甲马之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滨,今已两年。其安于羁苦,守节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穷;商略时事,则纤微皆察。国势安危,民情休戚,凡务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晓也。方值艰难之时,而使此辈人老身贫贱,亦可慨矣。”(同上)侯仲良自兵乱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滨”,当即在靖康、建炎之间,其“游荆门,胡文定留与为邻终焉”。正是在这一时期,胡宏拜侯仲良为师。
胡宏在《题吕与叔中庸解》一文中说:“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师圣,自三山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有张焘者,携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师圣笑曰:‘何传之误,此吕与叔晚年所为也。’……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师圣又夫子犹子夫也。师圣少孤,养于夫子家,至于成立。两夫子之属纩,皆在其左右。其从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其为人守道义,重然诺,言不妄,可信。”(《五峰集》卷三)由此可知,侯仲良为二程之舅的孙子,亦二程的侄女婿,他从小养于二程家,是跟从二程最久的弟子。依此关系,其“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当不是虚言。
胡安国、胡宏与侯仲良的密切接触至少有两年之久,湖湘学派对于“伊洛渊源”的认识当深受侯仲良的影响。侯仲良早年曾拜访过周敦颐,“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这对于北宋后濂溪著作的流传实具有关键意义。现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最早即出自侯仲良,而最早为其作“序”的就是胡宏。在胡宏作“序”的《通书》后,有祁宽写的《通书后跋》:
《通书》即其(周敦颐)所著也,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得之于高,后得之于朱;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传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周子全书》卷十一)
此“跋”作于绍兴甲子(1144),当时朱熹十四岁。祁宽是尹焞弟子,他先得《通书》于侯仲良所传之高元举,后得之于朱子发(震),又后来在尹焞门下得其所藏。侯氏和尹氏所传《通书》在卷末都有《太极图说》,而祁宽在九江周敦颐家所得旧本没有《太极图说》。“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或云”很可能出自侯仲良(若出自尹焞,则祁宽当直书其师之名)。尹焞是程颐晚年弟子,他所藏《通书》及《太极图说》乃“得之程氏”。但二程和尹焞等一直没有将《太极图说》示人,若无侯仲良所传,则朱震不可能于绍兴五年(1135)在所上《进周易表》中包括《太极图说》,而尹焞也仍可能将《通书》及《太极图说》藏不示人。倘若真如此,那么《太极图说》就可能湮没不闻,而朱熹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伊洛渊源”的开山之作。
侯仲良“有《论语说》及《雅言》一编,皆出衡山胡氏”。胡宏早年还编有《程氏雅言》,现传《五峰集》中有胡宏所作《程子雅言前序》和《后序》,这两篇序文不仅高度肯定了二程接续孟子以后失传的儒家道统,而且将其与王安石、苏轼和欧阳修之学做比较,认为王、苏、欧阳之学各有所偏,只有“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实生之,当五百余岁之数,禀真元之会,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五峰集》卷三《程子雅言后序》)。胡宏辨别北宋各学派的不同特点,他要继承和发扬二程的洛学,这是十分明确的。不仅如此,胡宏还最早提出了始自濂溪的道学(理学)谱系,这对于朱熹有重要的影响。其《周子通书序》云:
《通书》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五峰集》卷三)
这篇序文明确了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的地位,高度评价周敦颐之功“盖在孔孟之间”,又说《通书》“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这为此后朱熹最终确立周敦颐的理学之开山地位奠定了基础。
胡宏不仅表彰周敦颐之学,而且表彰邵雍和张载之学,从而提出了“北宋五子”的道学谱系。他在《横渠正蒙序》中说:
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先生名载,字子厚……与二程子为至交。知礼成性,道义之出,粹然有光,关中学者尊之,信如见夫子而亲炙之也。……著书数万言,极天地阴阳之本,穷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说而正人心,故自号其书曰《正蒙》。其志大,其虑深且远矣。(《五峰集》卷三)
胡宏在这篇序中将周、邵、二程和张载并列,此即“北宋五子”的谱系,亦即朱熹所编《伊洛渊源录》的谱系。据朱熹所说,《伊洛渊源录》中有邵雍是“书坊自增耳”(《语类》卷六十),但这也正说明胡宏提出的这一谱系的影响之大,朱熹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只是在《近思录》中排除了邵雍)。
胡宏作《横渠正蒙序》的时间大约在作《周子通书序》稍后。湖湘学派重视《正蒙》,自胡安国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著录“《正蒙》书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亦著录“《正蒙》书十卷”,解题云:“崇文校书长安张载子厚撰,凡十九篇……又有待制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按,晁、陈两书所录“《正蒙》书十卷”,当即胡宏在《横渠正蒙序》中所说“今就其编,剔摘为内书五卷、外书五卷”的合编。胡安国所传的《正蒙》一卷,可能是其选编的《正蒙》语录。概言之,《正蒙》在南宋初期的流传,亦如《通书》及《太极图说》的流传,与胡氏父子有密切的关系。
四、朱子集“濂洛关闽”之大成
朱熹说:“熹自十四五时得(二程和张载)两家之书读之”;又说:“熹自蚤岁既幸得其(周敦颐)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按,朱熹十四岁时即祁宽写《通书后跋》的绍兴甲子年(1144),朱熹初见李侗是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四年后乃正式受教于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将周敦颐的《通书》寄予李侗,李在回信中说:
承惠示濂溪遗文……极荷爱厚,不敢忘,不敢忘。迩书向亦曾见一二,但不曾得见全本,今乃得一观,殊慰卑抱也。……尝爱黄鲁直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延平答问》)
朱熹所寄《通书》,当即《太极图说》附于《通书》卷末的版本。李侗肯定《通书》,亦如他对朱熹的一贯教导,是从内心存养以观气象的角度加以肯定。
李侗于隆兴元年(1163)逝世。三年之后,朱熹有“丙戌之悟”(所谓“中和旧说”),此“悟”就是受湖湘学派的影响,认为“性”是未发,“心”是已发。在“丙戌之悟”的当年,朱熹编成《周子通书》,此为《通书》的长沙本,即依胡宏所定章次,《太极图说》仍附于末章的版本。乾道四年(1168),朱熹校订二程的《遗书》《外书》《文集》和《经说》等著作。通过对二程关于心、性、情的诸种说法进行反复思考,朱熹又有“己丑之悟”(1169,所谓“中和新说”),放弃了“中和旧说”的以心为已发的观点,而改为“心”有体有用,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心统性情”是也。朱熹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语,与横渠‘心统性情’相似。”(《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论心,惟《答吕与叔书》最后一篇为尽。而张子所谓‘心统性情’亦为切要。”(《四书或问》卷三十六)。“己丑之悟”是朱熹的思想臻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在“己丑之悟”的同年,朱熹重编周敦颐的《太极通书》。这次重编对于朱熹确立“伊洛渊源”的道学谱系和其本人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
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太极通书后序》建安本)
朱熹把《太极图说》移到《通书》各章之前,其文献依据就是潘兴嗣(清逸)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叙周敦颐著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其深意是他认识到濂溪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且二程“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如前所述,二程的《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所好何学论》实际上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中“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二程不言“无极”和“太极”,亦不言从“太极”到“两仪”的天地分化过程。而朱熹在此所谓二程“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实已把二程以及道南学派的心性理论上达于本体—宇宙论,并且把二程之“理”解释为“太极”。
从乾道六年(1170)到乾道八年,朱熹经过与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往复商榷,修改完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和《西铭解》。在《太极图说解》中,朱熹强调:
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
这是以二程的理本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阴阳”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在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中是没有的,朱熹以“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释之,对“两仪”没有明确的解释,后来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两仪是天地,与画卦两仪意思又别。……方浑沦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间放得宽阔光朗,而两仪始立。”(《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朱子语类》卷一)这与二程的理本论不讲“太极生两仪”,而多从“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讲起,是不同的。
朱熹把《太极图说》作为“伊洛渊源”的开端,使他所诠释的理本论思想更多地加进了宇宙论的内容。在《太极图说解》中,朱熹肯定了程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故在“理气先后”的问题上没有提出“理生气”或“理在气先”之说。但张栻《答朱元晦》信中有云:“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南轩集》卷二十)吕祖谦《与朱侍讲》信中也说:“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说解》……所先欲请问者,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先体后用,先显后微之说,恐当时未必有此意。”(《东莱集》别集卷七)观此可知,在朱熹的原稿中本有“体用先后”之论。朱熹在同时期写的《答杨子直》信中也说:“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11],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在改定的《太极图说解》中已无“体用先后”之论,朱熹在《答杨子直》信中也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但朱熹在《太极图说解后记》中针对“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批评说:“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观此可知,朱熹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理生气”,但在他的思想中实已内蕴了“先有此(理)而后有彼(气)”的观点。
此后,朱熹在与陆九渊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中提出:
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
所谓“在无物之前”“在阴阳之外”即已包含了“理在气先”的思想,故黄宗羲评论说:“此朱子自以理气先后之说解周子。”(《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陈来说:“朱陆之太极辩……标志着朱子理在气先思想的明确形成。”[12]朱熹晚年倾向于理对气的“逻辑在先”说,即所谓:
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子语类》卷一)
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
所谓“本无先后之可言”,是讲理气在时间上无先后;所谓“也须有先后”,是讲理的“逻辑在先”性,理终归是气的“本原”。朱熹在《答赵致道》信中说:“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朱熹的世界本原论,即是以“理”为本原的本体—宇宙论。
朱熹在作《太极图说解》的同时也完成了《西铭解》(在《西铭解》中贯彻了《太极图说解》的思想)。这两部书标志着在朱熹的思想中“伊洛渊源”道学谱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朱熹本人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乾道九年(1173),朱熹编成《伊洛渊源录》;两年之后,即淳熙二年,朱熹与吕祖谦合编成《近思录》。在《近思录》中,收入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624条语录,分为十四卷。其首卷讲“道体”,开篇就全文录入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此统率二程与张载所言的“道体”,然后又分设“为学大要、格物穷理、存养、改过、齐家、出处、治体、制度、处事、教学、警戒、辨异端、圣贤气象”等纲目。这样就把周、张、二程之学统合为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实际上也就是朱熹的思想体系,换言之,即是“濂洛关闽”的思想体系。
在编成《近思录》的两年之后,即淳熙四年(1177),朱熹又完成了他精心撰著的《论孟集注》及《论孟或问》。先此,朱熹在完成《太极图说解》和《西铭解》的乾道八年(1172)已编成《论孟精义》,此书“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解释《论语》《孟子》之“精义”。五年之后,朱熹撰成《论孟集注》。关于《精义》与《集注》的区别,钱穆先生论之曰:
至朱子四十三岁,又成《论孟精义》……此时朱子在大体上,仍是从程门上窥二程,从二程上窥孔孟。惟于程门诸儒,已渐悟其有失师旨。
至朱子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或问》成书。此时,朱子已认《精义》中说得没紧要处多,故只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门人诸家说多所摆弃。13]
所谓“朱子始自出手眼”,就是在朱熹完成了对“伊洛渊源”道学谱系的诠释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乃自出己意而作《论孟集注》。
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署为淳熙己酉(1189)作,而此两序“是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所作的序修改而来”。[14]依此说,朱熹的《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都作于淳熙初年,它们与《近思录》是同一时期的著作。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语类》卷一〇五)所谓“四子”不仅是指孔、曾、思、孟所作的《四书》,实际上还包括了朱熹为《四书》作的《集注》。在此意义上,亦可谓:“《四书集注》,乃《六经》之阶梯;而《近思录》,乃《四书集注》之阶梯。”也就是说,若要理解儒家的《六经》,乃须通过《四书集注》;而朱熹所编《近思录》,即他对周、张、二程思想的诠释,乃成为他“自出手眼”而作《四书集注》的阶梯。
《宋元学案》说朱子的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这是与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形成了“濂洛关闽”的思想体系相联系的;钱穆先生说宋代的“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15,这也是以朱子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为其主要标志的。
(原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
朱熹的社仓设计及其流变
⊙陈支平
朱熹设立社仓,是中国救荒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南宋之后,人们对于社仓的践行,大多声称源仿于朱熹的社仓之设。因此,深刻分析朱熹对社仓的设计与实践过程及其对于后世深远影响的分析,无疑有益于进一步了解朱熹关注民生的儒家情怀,以及南宋以来社仓的演变过程。
一、朱熹对于社仓的设计与实践过程
朱熹于乾道年间在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率先创立社仓,根据其后来撰写的《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的记述,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来,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
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而王公曰:“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刘侯与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请著为例。”王公报皆施行如章。
既而王公又去,直龙图阁仪真沈公度继之。刘侯与予又请曰:“粟分贮民家,于守视出纳不便,请放古法,为社仓以储之。。不过出捐一岁之息,宜可办。”沈公从之,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于是得籍坂黄氏废地,而鸠工度材焉。经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为仓三,亭一,门墙、守舍,无一不具。[1]
根据以上记载,乾道四年(1168),当地发生饥荒,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朱熹与当地的士绅刘如愚等主持乡里的发粟赈灾。经过这次赈灾的实践,朱熹意识到民间缺乏救灾储备的弊病,以及民间配合官府救灾赈济的重要性。于是,朱熹与刘如愚等一方面向当地官府建议充分发挥官府储备仓廪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策划由当地民间自行建设救荒仓库,配合官府常平义仓的米粮散敛制度,实行灾荒时期的自救活动。最终在当地官府的资助之下,“沈公从之,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经过4个月的努力,于乾道七年八月竣工,“为仓三,亭一,门墙、守舍,无一不具”,是为“社仓”。
朱熹和刘如愚等士绅所创立的崇安县开耀乡的社仓,至少在朱熹在世之年是十分成功的。根据朱熹在晚年的追述,社仓不仅较好地起到赈济灾荒的作用,而且由于管理得当、维持有术,其积谷也不断更新,时有增益。如《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载:“始予居建之崇安,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2]
淳熙八年(1181),朱熹在浙江任上的时候,适逢浙江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全力组织救灾救荒的同时,朱熹意识到储粮救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向朝廷上报自己在十年前举办社仓的经过、所定事目条款及其效应,该上奏文约有2000余字,兹摘引如下:
宣教郎、直秘阁、新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今具社仓事目如后: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保簿重行编排。其间有停藏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之人隐匿在内,仰社首队长觉察,申报尉司追捉,解县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断罪。次年三月内,将所排保簿赴乡官交纳。乡官点检,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户一口不实,即许人告,审实申县,乞行根治。如无欺弊,即将其簿纽算人口,指定米数,大人若干,小儿减半,候支贷日,将人户请米状拖对批填,监官依状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陈未接之际,预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给贷。仍乞选差本县清强官一员,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来,与乡官同共支贷。
一、申府差官讫,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远后近,一日一都。晓示人户,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阙,不得请贷。各依日限,具状。状内开说大人小儿口数。结保,每十人结为一保,递相保委。如保内逃亡之人,同保均备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仓请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队长、大保长并各赴仓识认面目,照对保簿,如无伪冒重叠,即与签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听。其日监官同乡官入仓,据状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实,别有情弊者,许人告首,随事施行。其余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给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斗,每桶受米五省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监官、乡官人从,逐厅只许两人入中门,其余并在门外,不得近前挨拶,挽夺人户所请米斛。如违,许被扰人当厅告覆,重作施行。
一、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官米,即开两仓,存留一仓。若遇饥歉,则开第三仓,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民,庶几丰荒赈贷有节。
一、人户所贷官米,至冬纳还。不得过十一月下旬。先于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将带吏斗前来公共受纳,两平交量。旧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虑仓敖折阅,无所从出,每石量收三升,准备折阅及支吏斗等人饭米。其米正行附历收支。
一、申府差官讫,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纳。先近后远,一日一都。仰社首、队长告报保头,保头告报人户,递相纠率,造一色干硬糙米,具状,同保共为一状,未足不得交纳。如保内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备纳足。赴仓交纳。监官、乡官、吏斗等人至日赴仓受纳,不得妄有阻节。及过数多取。其余并依给米约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贷日不可差换。
一、收支米讫,逐日转上本县所给印历。事毕日,具总数申府县照会。
一、每遇支散交纳日,本县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仓算交司一名,仓子两名。每名日支饭米一斗,约半月。发遣裹足米二石,共计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贴书一名,贴斗一名,各日支饭米一斗,约半月。发遣裹足米六斗,共计四石二斗。县官人从七名,乡官人从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饭米五升,十日。共计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计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两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盖墙并买蒿荐、修补仓廒约米九石,通计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社仓支贷交收米斛,合系社首、保正副告报队长、保长,队长、保长告报人户。如阙队长,许人户就社仓陈说,告报社首,依公差补。如阙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书锁钥,乡官公共分掌。其大项收支,须监监官签押。其余零碎出纳,即委乡官公共掌管,务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别生奸弊。
一、如遇丰年,人户不愿请贷,至七八月而产户愿请者听。
一、仓内屋宇什物仰守仓人常切照管,不得毁损及借出他用。如有损失,乡官点检,勒守藏人备偿。如些小损坏,逐时修整。大段改造,临时具因依申府,乞拨米斛。
具位朱熹奏节文:一、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其法可以推广,行之他处。欲望圣慈行下诸路州军,晓谕人户,有愿置立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付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随宜立约,实为久远之计。其建宁府社仓见行事目谨录一道进呈,伏望圣慈详察,特赐施行。3]朱熹关于社仓的上奏文很快就得到朝廷的批复,准予施行天下。《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九十九附有朝廷“敕命”云:
行在尚书户部准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饬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户部状,准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书省送到宣教郎、新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同共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窃谓其法可以推广,行之他处。而法令无文,人情难强。妄意欲乞圣慈特依义役体例,行下诸路州军,晓谕人户,有愿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与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计。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则亦不至搔扰。”[4]
为此,朝廷户部还规定了比较详细的常平仓、义仓存米的敛散办法:
本部今检准绍兴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项,诸州常平钱谷及场务钱不足,申提举司,通一路之数移用,仍听互相兑便支拨。诸义仓附常平仓监专兼管,敖屋以转运司仓充其积藏,而应兑换者准常平法。诸义仓计夏秋正税,每一斗别纳五合。同正税为一钞,不收头子、脚乘钱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仓。即正税不及一斗,并本户放税二分以上,及孤贫不济者,免纳诸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县遇灾伤,当职官体量,自第四等以下阙食户给散。若放税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给。并预申提举司审度,行讫奏。诸灾伤计一县放税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户乏种食者,虽旧有欠阁,不以月分,听结保贷借。即谷不堪充种子者,纽直以钱,各成贯石,给限一年,随税纳,仍免息。……如愿依上件施行,仰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有行义者具状赴本州县自陈,量于义仓米内支拨。其敛散之事,与本乡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并不须干预抑勒。[5]
综合以上朱熹的上奏文及朝廷的饬命文,大体可以知道朱熹所倡导的社仓是一种官府与民间协作运行的粮食救荒形式。民间出资在自己的乡里建造社仓,而官府从常平义仓中拨借米谷给社仓,或借出钱文给社仓籴买米谷,从而改变以往常平仓米、义仓米只能赈济州县城郭附近灾民的被动局面,而把常平米向穷乡僻壤散发,惠及全境的贫困百姓。社仓根据春夏借出、秋冬纳还的原则,向需要借贷的乡民接济度荒的粮食。如此则官粮、官钱不亏,民间也可比较平稳地度过青黄不接的时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熹所设计的社仓还有着一系列相互配套的事目条款。
首先,为了防止舞弊行为,民间在设立社仓的同时,必须先清理当地的户口,重新编排保簿。“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保簿重行编排。其间有停藏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之人隐匿在内,仰社首队长觉察,申报尉司追捉,解县根究……次年三月内,将所排保簿赴乡官交纳。乡官点检,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户一口不实,即许人告,审实申县,乞行根治。”在落实了当地的实际户口之后,才能指定米数,结算人口,实施赈给。
其次,对于管理社仓的人选,即社首、保正副、队长、大保长等,必须差使“本乡土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敛散之事,与本乡耆老公共措置”。也就是说,主持社仓的人选,基本上是以乡居的士绅为主,加上一些在乡里有声望的“有行义者”。如朱熹和刘如愚主持崇安县开耀乡的社仓建造之后,朱熹所推荐的管理社仓人选大多是刘如愚的族人。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说:“既成,而刘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请曰:(刘)复与得舆皆有力于是仓,而刘侯之子将仕郎琦尝佐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职郎玶亦廉平有谋,请得与并力。府以予言悉具书礼请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与讲求仓之利病,具为条约。”[6]“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7]朱熹认为社仓管理人选关系到社仓及救荒事宜能否得以成功的大事,必须有德高望重的士人们主持。他在《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中说:“常平者,独其法令簿书筦钥之仅存耳,是何也?盖无人以守之,则法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于所谓社仓者,聚可食之物于乡井荒闲之处,而主之不以任职之吏,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聪明仁爱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数公者,相与并心一力,以谨其出纳而杜其奸欺,则其法之难守,不待已日而见之矣。”[8]社首等管理人员名单的确认,最后还要经过官府审核批准,“即申尉司定差”。每次敛散社仓米谷之时,一般都有官府派下的吏员监督,“簿书锁钥,乡官公共分掌。其大项收支,须监监官签押。其余零碎出纳,即委乡官公共掌管,务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别生奸弊。”
最后,为了确保官府借出的常平义仓米谷不致损失缺额,社仓事目中还规定了米谷借出后至秋冬纳还时所应当加收的息米或耗米。“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但是如果遇到严重灾年之时,一般平民百姓交纳息米相当困难,事目又规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息米可以酌情减免,“人户所贷官米,至冬纳还……旧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虑仓敖折阅,无所从出,每石量收三升。”“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由于规定了比较合理的还纳加息条款,不仅可以基本保证官米不失,而且还有可能不断增加社仓的存谷,储蓄日丰。朱熹的五夫社仓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
从朱熹的社仓设计中可以看出,由于是官府与民间协作办理的体制,其社仓事目既考虑到官府对于社仓的监督作用,又规定了社仓的管理人选必须是当地的士绅及有行义者,两者相互配合、相互牵制;同时还兼顾到官府和民间的经济效益问题,既要使社仓发挥赈济贫困、储蓄备荒的功能,又不能让官府的常平义仓缺额亏本。朱熹的这种社仓设计,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效果与功能,难怪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历代人们的关注和效仿。这一设计充分反映了朱熹在民生理念上的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向朝廷奏请把自己的社仓模式推广于天下诸路州军时,其社仓设置之初的米谷来源,是政府的“常平仓”,但是到了户部批复时,则变成了“义仓”。南宋时期“常平仓”与“义仓”的存谷来源是有区别的。根据李华瑞的研究,常平仓米,“其籴本主要是留用地方上供钱支出,‘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后二三千贯,付司农司系帐。三司不问出入,委转运使并本州委幕职一员专掌其事。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9]这就是说,常平仓米事由上供财政款中截留地方使用的份钱中支用,属于政府财政预算内的开支。义仓米则不同。“义仓粮食的来源是各州属县于‘两税每石别输一斗贮之。’……义仓令主户于‘夏秋正税外每一石别纳一斗,随常赋以入。’”[10]也就是说,义仓内的米谷存储属于正税之外的附加。如此一来,朱熹原先的设计是由官府财政钱谷中出借社仓的“元本”,而到了户部的批复“饬命”中,则成为以“义仓”的名义向愿意设置社仓的乡村加收额外的税款,“诸义仓计夏秋正税,每一斗别纳五合。同正税为一钞,不收头子、脚乘钱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仓。”户部堂而皇之地把原先应属政府财政支出的常平仓米转化为加收额外税的义仓米支借给社仓,社仓赈济的重担最终试图转嫁给社仓所涵盖的一般民众。而从地方官的角度看,义仓加收社仓本米,不啻是加赋。担负加赋之名是一般地方官员比较忌讳的事情,于是大多数地方官员对于设置社仓的态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作壁上观,省得招惹麻烦。即使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多收税额总是坏事,灾害是否来临尚未可知,眼前就要多交税额,心理不好承受。由此看来,淳熙八年朝廷批准朱熹的社仓奏请推广于天下,基本上是表面文章,口惠实不惠。
二、南宋时期社仓实施的基本情况
朱熹对于宋孝宗批准自己的社仓建议,十分高兴,他在抄录朝廷饬命文之后送撰写的《跋语》中说:“往岁里中妄意此举,所以收恤隐民者,盖偶合其微指。顾以国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远及,且惧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遍下郡国,将遂得与阖宇之间含生之类均被仁圣之泽于无穷,固已不胜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积,又得上为明诏之所称扬,下为四方之所取则,抑又有荣耀焉。”11]因此,他又发动管辖之下的州县,赶紧施行,亲自写了《劝立社仓榜》,告示属下官府及民间,该榜文云:
当司恭奉圣旨,建立社仓,已行印榜,遍下管内州县劝喻。寻据绍兴府会稽县乡官、新嘉兴主簿诸葛修职名千能状,乞请官米置仓给贷。而致政张承务名宗文、新台州司户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龙游县袁承节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谷置仓给贷。当司契勘前件官员心存恻怛,惠及乡闾,出力输财,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挥具申朝廷外,须至再行劝勉,量出米谷,恭禀圣旨,建立社仓,庶几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有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再此劝喻,各请知委。12]
朱熹的社仓设计虽然于淳熙八年十二月由朝廷批准向全国推广,但是其实际施行的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关于这一点,朱熹曾经多次提到。如《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载:“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社仓),因得条上其说。而孝宗皇帝不以为不可,即颁其法于四方,且诏民有慕从者听,而官府毋或与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13]《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中亦云:“始予居建之崇安,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中间蒙恩召对,辄以上闻,诏施行之,而诸道莫有应者,独闽帅赵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为能广其法于数县,然亦不能远也。”[14]
其实,朱熹所创立的社仓法虽然有朝廷予以推广的谕令,但不能在当时的各个地区施行,是与南宋的社会经济及政府财政状况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仓法是一种由官府和民间相互协作而成的救荒形式,这就需要具备两种基本条件。一是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民间有较为宽裕的粮食剩余以及储备;二是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各地官府能够在上供财政和日常财政支出之外,尚有余钱余谷来向民间出借,从而保障民间社仓的正常运转。但是在朱熹所处的时代,这两个方面都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由于宋代实行基本上“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社会诸等级对土地的占有是极为悬殊的。根据漆侠的研究,宋代经历了三次土地兼并的高潮。其中,第三次兼并高潮在南宋初年就出现了。这次兼并土地的高潮,从宫廷到民间,从临安到地方,到处兴起,官僚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州县寓官,候补等缺之余,以兼并土地为事。[115各阶级阶层对土地的占有情形为:“占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的地主阶级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其中占总人口千分之四五的大地主占田竟达百分之四五十,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过是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下。”[16
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官府册籍混乱、经界不清,一般的贫苦农民虽然占地很少,但是政府的各种赋税却大部分转嫁到他们身上,痛苦不堪。前述朱熹一直以清经界为己任,就是深刻地认识到南宋时期土地兼并对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当然,在南宋的大环境之下,朱熹的这一愿望是很难实现的。社会资源占有的严重不公平,加上南宋朝廷所管辖的地域比较狭小,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南宋时期的政府财政始终处于困难之中。“南宋是在兵荒马乱中建立起来的,又是在硝烟弥漫中被摧垮的。”兵连祸结,靡有已时。因而财政开支浩大有其客观原因,“但更加主要的是财政开支之滥施是由于南宋统治的腐败”。[17]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压力,南宋政府基本上是在两税征收中采取了压榨广大自耕农民的财政政策,两税征收大幅度地增加起来,特别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更是让平民百姓不胜其扰。
在这种一般下层百姓穷困潦倒、政府财政窘迫的困境之中,政府要实施有效的社会救助措施,就显得相当困难。宋代设有“常平仓”“义仓”等制度,原意是政府储备一定数额的余粮,在发生自然灾害等不时之需时,政府散发常平仓、义仓中的粮食,救济受灾民众。从制度上说,这类属于应急灾荒的常平仓、义仓储备粮食是“不得他用”[18]的。但是到了朱熹的时代,常平仓、义仓中的存粮,经常被官府的其他通途所挪用。朱熹为此一再上奏朝廷,谴责那些挪用常平仓米和义仓米的官员,要求朝廷予以惩治,但是朝廷深知这些常平仓米、义仓米的所谓用于“赈济”,只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因此对于朱熹的上奏文,基本上装聋作哑、不予批复。如朱熹在浙江任上,对于地方官员把常平仓米作为“官兵米”散给,相当气愤,他在《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中云:
照对臣昨据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崈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适当荒歉之后,财计匮乏,别无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于丰储仓内更给助米二万石,以济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余石,未有指拟,逐急于常平义仓米内权行借兑,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赐处分施行外,申本司照会。……去后又据衢州申,再行借兑义仓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粮米。……臣伏缘在法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违制论。……意谓朝廷必须薄行责罚,以戒后来。今乃一无所问,亦不略行戒约,即在本司,何以约束诸郡?19]
然而让朱熹更为气愤的是,上奏文呈递上去之后,擅自借兑常平仓米的官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越支越多,朱熹只好再次上呈《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义仓米状》云:
衢州沈崈一违法擅行借兑过常平义仓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下衢州,督催补还元旧窠名,及具录奏闻,乞将本州当职官略行责罚,以戒将来,未得回降。今来再据衢州沈崈一申,又于常平米内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军粮,三个月共擅借过一万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过常平米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亦系充官兵俸料,未曾拨还。及称目下盘量折欠米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项共计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臣照对在法义仓谷唯充赈给,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违制论……而本州略无忌惮,甚非朝廷置立常平之意,窃虑必有情弊。……欲望圣慈先将衢州违法擅支常平义仓米当职官吏特行责罚,以警诸郡,为擅用常平义仓米者之戒。[20]
不仅衢州如此,婺州也是如此,经过数次支借之后,常平仓内存米仅剩7000余石,但是官员还向朝廷申请再挪2万石,竟然得到朝廷的批准。这就不单单是挪用常平仓米的问题,地方掌管财政的官员不得不东挪西借,把其他方面的开支钱谷暂时拿来应付“支遣军粮”了。朱熹在《乞降旨令婺州拨还所借常平米状》中说:
臣伏准尚书省劄子,备据知婺州钱佃奏,乞于本州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支借二万石支遣军粮。八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许支借二万石,限至岁终拨还。臣除已恭禀施行外,臣窃见义仓米在法唯充赈给,不许他用。今岁婺州诸县例皆旱伤,将来细民必致阙食。……先来本州已曾借过一万七千石,元降指挥,候秋成先次拨还,尚未还到颗粒。今来再借二万斛,止存七千余石,已是不足支遣。……欲望圣慈,特降指挥,令婺州将两次借过米三万七千石趁此秋成,尽数先行拨还,庶几可以添助赈济。[21]
这些奏请基本上没有取到朱熹所预期的效果,常平仓米、义仓米被地方官府挪作他用的情景不断发生。[22这就大大降低了常平仓、义仓原先所设计的基本功能,逐渐沦为政府应急财政的一个储备口。再加上有些地方官吏的怠政行为,加剧了常平仓、义仓的某些弊病。如有些官吏对于常平仓疏于日常管理和运作,致使常平仓内的存谷、存米腐败变质、无法食用;有些常平仓常年关闭,无人问津,无法惠济灾民。朱熹在江西任上以及福建等地,都看到了这种情景。其中,江西的情景为:
所有本军(南康军)城下常平仓见椿管口口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石二斗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月内盘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石三斗二升四合外,实管见在米七千八百三十石九斗四升一合二勺。系是乾道八年以后逐年收籴到数目,价钱不一。其米经年在敖,内有结冒陈损。兼照今年七月内,管属建昌县阙少米斛出粜,所支拨义仓米估价应接民间食用,每升计价钱一十文足。已具收报提举使衙门照会去讫。所有见管和籴米,本军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经年陈损,与受纳到人户义仓米陈损色样一同,依市价每一升估计价钱一十文足本军照得上件米系是当来委官和籴到数目,且虑亏损元价,未敢擅便出粜。23
福建的情景为:
“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24]
由于无法保障常平仓米、义仓米的充足供给支借,再加上朝廷对于社仓建议所采取的是“口惠实不惠”的敷衍态度,义仓所存米谷的责任推还给基层百姓,设置社仓,须先加赋,造成许多地方百姓对于建立社仓的意愿相当低下,许多地方官就只能对于淳熙八年推广社仓的谕令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了。因此,朱熹的社仓设计虽然得到宋孝宗的批准,推行于全国,但是并没有在当时形成行政制度上的施行。
台湾学者梁庚尧曾经广泛搜集南宋时期的社仓资料,统计出社仓建议在朱熹之后有很大发展,共有记载64处之多。“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西、湖南、四川、广南、淮南各地,可说是几乎遍布南宋各区。”但是这些社仓的出现并非主要由政府的行政制度所促成,而主要是一些地方人士和官员仰慕朱熹的道德理念所促成的。梁庚尧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各社仓的创办人,如诸葛千能、张洽、李燔、赵师夏为朱熹门人,真德秀、赵景纬为朱熹再传弟子,万镇为三传弟子,魏了瓮、李道传、李大有则为私淑朱熹之学者;其他如陆九韶为陆九渊的家兄,和朱熹是时相论学的好友,丰有俊为陆九渊门人,刘宰为张栻再传弟子,潘景宪为吕祖谦门人,也都是理学同道。可知社仓的推广,朱熹门人和理学同道出力甚多。”[25]而从社仓的地理分布上看,以朱熹长期讲学的福建以及朱熹的过化地区最多,仅福建就有11个州县施行,几占南宋各地社仓的五分之一。因此,从梁庚尧的统计数字中,我们看不出当时政府在行政制度上对于社仓施行的保证与推行,南宋社仓的设置,基本上是个案性的、道德性的传播。上面引述朱熹本人对于当时社仓难于推广的叹息,即所谓“至今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今几三十年矣……诏施行之,而诸道莫有应者……然亦不能远也”,可能更为接近南宋社仓的基本事实。
当然,社仓难以在南宋推广,归根到底在于社会经济的不振与政府财政的困窘。南宋朝廷即使有意愿从行政制度上在全国推行社仓,也只能通过“义仓”加税的办法来施行。然而这种加税的办法,恰恰又阻碍了从行政制度上推行社仓的可能性。不仅南宋如此,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凡是救荒政策实施得比较得力的年代,基本上是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如康雍乾时期号称“盛世”,也是社仓等比较繁盛的时期。[26]反之,到了清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社仓之举也就逐渐沦为名存实亡的状态。
三、朱熹社仓的影响与流变以及清代社仓的繁盛
朱熹所提倡的社仓,虽然在南宋时期未能得到较为广泛的施行,但是其历史影响却是十分深远。迄至明清时期,凡举办置仓救荒之策,大多要提到朱熹的社仓设计。特别是到了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国家财政相对宽裕,民间也往往有所盈余,在三位皇帝的推动下,朱熹所设计的社仓模式得到了空前发展。可以说,朱熹的社仓设计未能在南宋时期得到有效的施行,在明代也是时有时无,无法形成整体性的社仓氛围。唯有在清代的康雍乾时期才得到比较全面的践行。然而,如果进一步对朱熹设计的社仓制度与明清时期的社仓实施情况做更深入的比较,还是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
如上所述,朱熹在崇安县开耀乡设置五夫里社仓时,其米谷是从官府的常平仓或义仓中支借出来的,淳熙八年朱熹向朝廷奏请向天下推广社仓设置时,提出了以向官府支借米谷为主、辅以富家捐助的兴建社仓的建议。所谓“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同共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日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与拨还。”[271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南宋时期有限的关于社仓的记载,证实当时社仓开设之初的米谷来源,是以向官府支借为主、民间捐助为辅作为基本形式的。如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中说到的大阐社仓最初的米谷来源是官府。由于原仓地址设置不合理,更改位置使得散敛更为方便。
招贤里大阐罗汉院之社仓,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为,而长滩之别贮也。始,秘阁魏君之筑仓于长滩……仓之所在,极里之东北,而距西南之境远或若干里,贷者多不便之。而是时率常数岁乃一往来,则犹未甚以为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发敛之政,而以岁贷收息之令从事。既为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时颁焉……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说告者……周君于是白于宋公,而更为此仓,以适远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输焉。来岁遂以远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岁得饱食,而又无独远甚劳之患,于是咸德周君。8]
福建浦城县的永利社仓也是如此。朱熹在《浦城县永利仓记》中说:
浦城县迁阳镇永利仓者,故提举常平公事黄侯某之所为也。闻之故老,某年中黄侯以乡人奉使本道,奏立是仓其里中,岁时敛散,以赈贫乏,且使镇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颇赖其利。后以兵乱废熄无余,岁或不收,民辄告病,于今若干余年……今知县括苍鲍君恭叔之来,乃复有请,而使者吴兴李侯沐深然之,于是鲍君得致其役。营度故壤,筑仓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旧制。。遂移县庾之粟若干斛以贮焉,夏发以贷,冬敛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仓制饬从事。[29]
福建邵武军光泽县社仓也是由官府支给,不过不是直接从常平仓中拨给米谷,而是从县财政的盈余之中,用籴米充实社仓,以及购置田产、籍没僧田等,以每岁所入米谷充实社仓。朱熹在《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云:
光泽县社仓者,县大夫毗陵张侯诉之所为也。适会连帅赵公亦下崇安、建阳社仓之法于属县,于是张侯乃与李君议,略放其意,作为此仓。而节缩经营,得他用之余,则市米千二百斛以充之。夏则捐价而粜,以平市估;冬则增价而籴,以备来岁。又买民田若干亩,籍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岁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仓,以助民之举子者如帅司法。既又附仓列屋四楹,以待道涂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栖托食饮,而无暴露迫逐之苦。盖其创立规模,提挈纲领,皆张侯之功。而其条画精明,综理纤密者,则李君之力也。[30]
朱熹曾撰写《常州宜兴县社仓记》,其中所谈到的社仓也都是由官府设置给谷,并由邑之贤者主持管理事宜。其中,朱熹高度赞扬了常州宜兴县知县高商老设置社仓,把官府常平仓的作用充分发挥于民间救荒之中。
绍熙五年春,常州宜兴大夫高君商老实始为之于其县善拳、开宝诸乡,凡为仓者十一,合之为米二千五百有余斛。择邑人之贤者承议郎赵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余人,以典司之。……会是岁浙西水旱,常州民饥尤剧,流殍满道。顾宜兴独得下熟,而贷之所及者尤有赖焉。……明年春,高君将受代以去,乃复与赵、周诸君皆以书来趣予文,且言去岁之冬,民负米以输者繈属争先,视贷籍无龠合之不入。予于是益喜高君之惠,将得以久于其民,又喜其民之信爱其上,而不忍欺也。31]
在朱熹所撰写的社仓记中,也有两篇记载社仓所存米谷是由民间士绅富户捐助的。《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云:
淳熙二年,东莱吕伯恭父自婺州来访余于屏山之下,观于社仓发敛之政,喟然叹曰:“……吾将归而属诸乡人士友,相与纠合而经营之。使闾里有赈恤之储,而公家无龠合之费,不又愈乎!”是时伯恭父之门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时已务赈恤,乐施予,岁捐金帛,不胜计矣,而独不及闻于此也,于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谷五百斛者,为之于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敛散以时,规画详备,一都人赖之,而其积之厚而施之广,盖未已也。[321
《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云:
是时南城贡士包扬方客里中,适得尚书所下报可之符以归,而其学徒同县吴伸与其弟伦见之,独有感焉。经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绍熙甲寅之岁,发其私谷四千斛者以应诏意,而大为屋以储之。……其为条约,盖因崇安之旧而加详密焉,即以其年散敛如法。乡之隐民,有所仰食,无复死徙变乱之虞。[33]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断言,南宋时期设置社仓之初的米谷基本上是以官府支借常平仓、义仓米以及利用财政盈余的款项籴米或购置田产等官出为主,而以民间捐助为辅。根据王文书研究,“从(笔者注:梁庚尧)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出,官方出资社仓占总数的52.3%,私人出资社仓占总数的23.1%,众人集资占总数的12.3%,官、众合资社仓占总数的6.2%,出资情况不详的占总数的6.2%。官方出资和官、众合资相加占到58.5%。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仓都经营借贷,但是从这一不完全抽样调查中可以找出这样一个规律:官方直接出资的社仓占有很大的比例。”[34]这里所说的官方出资,基本是沿袭朱熹的支借常平仓米,以及支借地方财政的赢余部分。至于户部提出的义仓存谷加收赋税的做法,地方官员普遍担心遭受加赋的谴责,目前很少看到这种做法的记录。况且,由于其致使当时的社仓未能得到行政制度上的普及,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仓设置之初支借米谷的主要来源。
到了明清时期,则有不同。社仓所存米谷,基本上是以民间捐助为主。《明史·食货志》记云:
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折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阵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35]
明代是施行社仓比较薄弱的朝代,但即使是从有限的试行过程的记述中,我们还是知道当时社仓的存谷全部来自民间,“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对于社仓之设都比较重视,加上这三朝的社会经济总体状况良好,所以朝廷推行社仓制度比较容易得到施行。但是从社仓设置之初的存谷情景看,也是以民间捐助为主要途径。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上谕云:
谕于各村庄设立社仓,以备饥荒。如直隶设立社仓,果有益于民生,各省亦照此例。嗣廷臣等议定,社仓之谷,于本乡捐出,即贮本乡,令诚实之人经管。上岁加谨收贮,中岁粜借易新,下岁量口发赈。[36]
康熙五十四年(1715)议定直省社仓劝谕之例:
凡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多捐一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绅衿能捐谷四十石,令州县给匾,捐六十石,知府给匾,捐八十石,本道给匾,捐二百石,督抚给匾。其富民好义,比绅衿多捐二十石者,亦照绅衿例,次第给匾。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部给以顶带荣身。凡给匾民家,永免差役。[37]
康熙年间社仓存谷由民间捐助的办法一直延续到雍正年间,但是在少数地方也出现了犹如南宋义仓加税派征的情况。对此,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1724)特地下道谕旨,强调社仓由民间捐助而不得于正税之外滥派的宗旨:
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则莫便于社仓。前谕尔等,劝导建设,盖专为安民起见也。尔等自应转谕属员,体访各邑士民中,有急公尚义之心者,使主其事。果掌管得人,出纳无弊,行之日久,谷数自增。至于劝捐之时,须俟年岁丰熟。输将之数,宜随民力多寡。利息从轻,取偿从缓。如值连年歉收,即予展限,令至丰岁完纳。一切条约,有司毋得干预。至行有成效,积谷渐多,该督抚亦只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使社仓顿成官仓,贻后日官民之患。朕初意如此,孰料该督抚欲速不达,令各州县应输正税一两者,加纳社仓谷一石。且以储谷之多少,定牧令之殿最。最近闻楚省谷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是为裕国乎?抑为安民乎?谕到该督抚速会同司道府等官确商妥议,务得安民经久之法以副朕意。
嗣复奉谕旨:社仓之设,原以备荒歉不时之需,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烦扰。朕以为奉行之道,宜缓不宜急,宜劝喻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是在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益,而无社仓之害。尔督抚当加意体察。至是议定社仓之法,一令地方官开诚劝谕,不得苛派米石。[38]
由上可知,清代的康熙、雍正年间,朝廷对于社仓的政策,都是以民间捐助米谷并由民间自主管理为主的。虽然也有少数地方官员试图通过正赋之外加派的方式筹集社仓的存量,但是被雍正皇帝发现之后予以禁止。除此之外,雍正年间也有少量像朱熹当年设置社仓那样,由官府的常平仓内支借部分米谷作为民间社仓本谷的,如云南省于雍正十三年定云南社仓之法:
云南设立社仓,通计一省所捐谷麦七万余石,其中十(千?)石以上者仅二十余处,此外皆数百石、数十石,亦有全无社谷者。至是议准云南各属皆有常平仓及官庄等谷存贮尚多,可酌量暂拨以作社本,将社仓存贮未及千石者,按地方之大小计存贮之多寡,于该处常平、官庄等谷内拨动五百石或八百石,作为社本,令社长一并经营出借穷民。秋成加一还仓,小歉免其取息,归于社仓项下积贮,俟积有千石,仍将原动常平等谷归还原款。[39
再如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求借用陕省火耗银8万两采买社仓谷麦,奉旨与甘肃巡抚石文焯商酌为之。[40陕西地方志也记载:“社仓,陕省向无社谷,雍正七年督院岳钟琪奏准,将应免五分耗羡银积存买粮,以作社本。”[41]不过就康熙、雍正年间的整体情景而言,这种官借社本的形式在清代前期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形式而已。
乾隆朝是清代最鼎盛的时期,乾隆皇帝对推行社仓制度特别用心,特别是强调在行政制度上予以保障和施行。在他的推动下,乾隆年间成为清代施行社仓最为繁盛的时期42j,也是宋代以来施行社仓最为繁盛的时期。为了使社仓的设置、管理以及敛散制度更为完善,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直省督抚地方官,开展对于朱熹《社仓事目》的大讨论。是年年底,御史朱续晫请将朱熹《社仓事目》发交各省督抚悉心讲究。十二月初一日上谕要求:“著各省督抚悉心详议具奏。”乾隆五年正月,户部咨文发给各省督抚。[43]于是在这一年,各省督抚纷纷把讲究的意见上折奏覆朝廷。这里,兹举闽浙总督德沛于七月初一日的奏覆为例。德沛按照朱熹《社仓事目》中的主要十一条目逐次检讨福建社仓的实施情况(在此略去朱熹《社仓事目》中的原条款)云:
一,《事目》内开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保簿重行编排……等因。查此条与保甲之法实相为表里,今保甲屡经严饬地方官实力遵行,其甲排甲册即事目所载保簿也。现行保甲烟户之下,原令开填户丁数目并作何生理字样,凡借贷给赈查照甲牌大小口核给,责成保甲长开报缴县察对,无伪给发,社长、社副依状支散,其逃军无行之人以及增添漏落之处,均难弊混。至所云乡官即今之社长、社副,名异实同,似可毋庸再设乡官,及编甲排甲册,应照现在条规遵行。
一,《事目》内开逐年新陈未接之际,预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给贷……等因。查委员监贷,原恐乡官蒙混而设,如果查系立品端方、乡间推重之人,充为社长、社副,又经立有劝惩之条,有过即惩,有善即奖,是劝惩明而商罚昭,则支贷自必公平,如再另委员役未免繁扰。况小县仅设一知一典,更难分身遍为监贷。此即朱子原札所云风土不同、随宜立约、申官遵守也。
一,《事目》内开申府差官讫,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等因……臣思欲收实效于日后,莫若立法于事先,应请先于造册时,细加区别,于人户之下注明士、农、工、商、不事生业五项,又于士、农、工、商之下注明需贷、不需贷,于不务生业下注明不、准贷各字样,支贷时即以此册为据,则扶同冒领之事无待临时稽查,互保自无弊混。
一,《事目》内开支收米用官斗,仰斗子依公平量。等因。查社谷出入原令均用官斗,兹应再饬令社长、社副各置升斗一副,送县较准,印烙发用,俾出入自可均平。
一,事目内开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官米,即开两仓,存留一仓,……等因。……应请酌量年岁之丰歉,计算人口之多寡,随时呈报上司,斟酌举行,庶事无拘泥而缓急有济。
一,《事目》内开入户所贷官米,至冬纳完……等因……至闽省息谷现准部咨,议准前署抚臣王士任条奏丰岁收息一斗,歉岁免息,已经通饬遵照在案,于仓谷、民生两便,其免二斗加三升之处毋庸再议。
一,《事目》内开申府差官讫,即一面出榜排定曰分,分都交纳……等因。……应令该州县于收放时剀切再行示禁,则自无守候、需索之弊。
一,《事目》内开收支米讫,逐日转上本县所给印簿,事毕具总数申府县照会……等因。……今再设印簿稽考,更为周备,亦当一体遵行,以重积储。
一,《事目》内开排保式甲户内开明大人若干口、小儿若干口……等因。查此条应即于保甲册内逐一编明,事属简便,可无弊混,似毋庸重复编造,以免纷扰。
一,《事目》内开队长阙社首依公差补,社首阙即申尉司定差。等因。查昔有队长、社首等项名目,今设社长、社副,酌古而不泥于古,虽今昔异名,其实总署一致,如有阙额,公择端方有品之人即行充补,以专责成。
一,《事目》内开簿书锁钥乡官公共分掌。等因。查收散社谷,州县设有印簿二本,一付社长收执,一缴州县存查,出入既有所稽,不经胥吏之手,自无滋扰之弊。互相稽查,深属得宜。再,查康熙十九年钦奉圣祖仁皇帝谕旨,义仓、社仓永免协济外郡,实为劝谕备赈之至要,自应敬谨遵守奉行。如地方官有抑勒、那借等弊,许社长、副以及捐输人户赴上司衙门呈控参处。庶官吏知儆,积贮充盈,俾严疆要地实有备而无虞矣。[44]
乾隆四年至五年,朝廷与地方督抚所进行的关于朱熹《社仓事目》的讨论,一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社仓设计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实推进了乾隆时期社仓的发展。综合各省督抚的讨论奏折来看,乾隆时期的社仓在各省已经普遍设立,社仓的设置与管理制度也较为完备。各省督抚在遵循朱熹《社仓事目》条款的同时,也会因地制宜适当调整某些措施,使得社仓的运行更为适合清代的实际情况。[45]
在乾隆皇帝的大力倡导之下,当时的社仓有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在乾隆前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财政的许可,各省督抚及地方官员也都努力在各地规划推动社仓的建设与施行。社仓几乎遍布全国各个行省,官府向民间社仓,尤其是一些边远地区和穷困地区社仓支借官本的现象有所增加,社仓的存谷数量也都较以往有所增加,有些地方的增加数量甚至相当可观。但是从整体上看,清代的康雍乾时期,民间捐助依然是社仓之谷的主要渠道。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宋邦绥在谈到该省的社仓存谷时说:“前任抚臣李绂题明动拨常平谷石借民收息,立为社仓谷本,嗣后酌定大、中、小州县分贮,自四千石以至三千石不等,名为社谷,实与常平无异,非如他省民自捐输者可比。”乾隆三十二年,江西巡抚吴绍诗也在奏折中说:“江西社谷向系捐自民间,现在每州县本息社谷,查据各属册报,自二三万石至六七千石,最少亦二三千石不等,通省共计七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余石,不为不多。”[46]从这些奏折中,我们不难看到乾隆年间社仓存谷来源的大致趋势。当然,清代是所谓“捐输”名目最多的时代,各种花样的“捐输”带有强迫性的意味很明显。清代社仓存谷的以民间捐助为主,其中带有强迫性的因素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在一些比较偏远以及穷困的地区,政府借本、出本设立社仓的现象也有所增加。无论是民间捐助,还是政府借本、出本,清代乾隆年间社仓的兴盛,都与政府在行政上的大力推行有着直接的关系。
乾隆年间的社仓设置与运作虽然达到宋代以来的最高峰,但是由于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一部分地方督抚及地方官员,往往投其所好,夸大地方设置社仓的实际效果,虚报社仓的数量以及社仓存谷的数量。致使在清查的过程中,时有发现社仓存谷与实际盘点数额不符的现象。如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朝廷派官员核查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嘉兴等地的社仓,就发现其中缺额者甚多,管理不善,“据窦光鼐奏,盘查过嘉兴、桐乡、海盐等六县仓谷,有缺谷数数百石及百余石者……桐乡县仓内实无储谷,所有之谷乃借自折仓;又借米三千石开报平粜,掩饰一时。嘉兴县折仓空虚,呈控纷纷,是该二县社仓办理皆不妥协。”[47]乾隆三十五年,清查苏州等富庶地区的社仓存谷,也发现册上之额与实际存粮数额的较大差距,“经查核,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属各社仓,应储之额虽有二十六万九千余石,严饬核实清厘,内中存价未买者有六万数千石,社长侵亏者六百余石,历年出借在民者一十六万三千余石,稽其实存在仓仅四万余石……责成巡道严行督催稽查,务必令悉归实储。”[48这些流弊越到乾隆晚年及其后越发严重。
再者,乾隆年间社仓的发展得益于乾隆皇帝及朝廷的强力推行,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就存在政府过多干预社仓日常运作的情景。康熙、雍正年间,社仓的运行情况一般不必题报政府,如上举雍正二年的谕令,“该督抚亦只可具折奏闻,不宜造册题报”。但是在乾隆年间,社仓数额及存谷数额不仅要题报朝廷,而且在散敛等诸多环节,都得经过官府的允许,“社仓既有报部之议,则经理须归有司之手”。[49]当地方官府在其他财政支出上出现困难时,就难免挪用社仓米谷来应急。如乾隆二十六年安徽省就想把社仓息谷挪用来修筑常平仓库,“安徽省现需修建仓廒,无款可动,请酌拨社仓息谷,变价以济工需。”[50]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江西巡抚郝硕奏请循福建等省成例酌变社仓息谷以充地方公用,他依据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间安徽、福建二省奏请,将社仓息谷变价解司,以充地方公用。“按其所存息谷数目,照依时价出粜,将价解司贮库。遇有农田、水利等务为民间必需工作势不可缓者,奏明动用,报部核销”,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山西也是如此,乾隆四十年布政使黄检为变通社仓义仓息谷变价解贮司库事上奏,“其余息谷三十五万八千七百余石,请令各州县于粮价稍昂之时详请价值,酌量售粜,事竣即将谷价解贮司库……并于要事公费均有预备动用之款。”[51]这样的变通是朱熹当年设计社仓时所万万未能想到的事情,已经超出了社仓备荒、救荒的初衷。
通过以上朱熹社仓设计及其流变的分析,不难看出:朱熹当年设计并亲自实践的五夫社仓,起到了备荒、救荒的社会功能,宋孝宗批准社仓建议推行于天下时,由于执政部门(即户部等)规定了社仓设置之初的官本必须在正税之外附加征收,大多数地方官员虚与应付,碍难施行,致使朱熹的社仓设计并没有得到行政上较为广泛的普及,而只有一些道德上的模仿。尽管如此,朱熹的社仓设计对于后世却影响深远,特别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当政者每每以朱熹的《社仓事目》为指南,大力推行社仓制度,在行政制度上予以相应的保障与施行,以至清代乾隆年间成为朱熹之后践行其社仓理念最繁盛的时期。换言之,南宋时期朱熹所设计的社仓制度是在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得到行政上的真正施行。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社仓制度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与朱熹原先设计条款所不甚一致之处。我们通过从南宋时期以至清代社仓的变迁历程,更可体会到朱熹所具有的长远文化精神。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又载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朱汉民
什么是义理之学?历史上,人们把那些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称为“义理之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代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人们的思想或者印象中,义理之学似乎就是一种对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义的体悟。义理之学成为脱离实际、空疏无用的知识学问。这和历史上义理之学的本义以及后来的思想发展完全相脱离。本文试图对宋儒的义理之学重新诠释,以求获得对义理之学的合理理解。
一、“义理”的本义
当清代学者将宋学定义为“义理之学”时,是为了与他们心目中的“汉学”区别开来。他们主要是以知识学意义上的学术范式差异来理解“义理之学”的“宋学”,即将“宋学”视为一种以道德义理的诠释、思辨为重点的义理之学,以区别于以文字、文献和典章制度为重点的考据之学。但是这与宋儒自己所理解的“义理之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宋儒称自己的学说为“义理之学”“理学”时,其意义首先是学术的社会使命与文化功能意义上的,即他们旨在恢复原始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旨在恢复与建构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圣学”以解决社会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问题。其次,“义理之学”“理学”当然也是学术范式、知识形态意义上的,“义理之学”的目的是要恢复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圣学”的文化功能,故其学术范式必须采取道德义理的诠释、思辨为重点的义理之学的学术形态。
从社会功能、学术范式的双重意义上考察宋儒“义理之学”,我们必须首先厘清:这个在文献典籍上耳熟能详的“义理之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所以必须进一步探讨“义理之学”中“义理”的历史含义。
“义理之学”是宋代出现的,而“义理”或者“理义”则是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同时在双字词“义理”“理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理”“义”的单字词,并且有了确切的哲学含义;至于单字“理”“义”组合而成的“义理”“理义”,则是其哲学含义的深化。
在先秦文献中,“义”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其词义也较丰富,但是,其主要意思则是正义、道义、德义相关的道德概念,涉及的是与人的道德价值相关的精神世界。人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诸多道德准则、道德范畴的一种,如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诸多德行、规范的根本准则。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说“义,群善之蕝也。”(《郭店楚墓竹简》,第179页)
在先秦文献中,“理”也是一个大量出现的词,与“义”主要是一种道德意义的价值概念不同,“理”最初就是一种法则意义的客观规律概念。据学者邓国光考订“理”最早见于典籍是动词“整理”“治理”的意思,“与治国的‘疆理天下’的重大事件相关”(邓国光,第6页)。由动词的“理”转化出名词的“理”,就具有了客观法则的意义。对于古人来说,客观法则的“理”可以是自然法则,即所谓“物成生理”(《庄子·天地》),“万物殊理”(《庄子·则阳》),“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韩非子·解老》);也可以是社会法则的理,即所谓“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墨子·非儒》)“故礼者,谓有理也。”(《管子·心术》)
在先秦文献中,当独立的“义”字、“理”字出现以后,又产生了将“义”和“理”连用的“义理”或“理义”。这种连用的“义理”的结合一般形成三种词组结构,并形成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理”与“义”并列义,如《墨子·非儒》有“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就是一种“义”与“理”的并列。所以《管子·形势解》说:“国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同时又指出:“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这里分别出现“理义”和“义理”,说明其“理”(法则)与“义”(道义)的并列关系。其二,是以“理”定义“义”的偏正结构。如孟子向来重视道义,多讲“义”,但偶尔也说“理义”,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孟子所说的“理义”,旨在强调“义”的内在必然性,故以“理”修饰“义”。其三,是以“义”修饰“理”的偏正结构。《管子·心术》说:“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管子重“理”,故而他说的“理”是社会法则,他特别强调“理”的法则必然决定“义”的道义应然。
在先秦诸子中,大多都要讲“义”“理”或者“义理”。但是,先秦儒家重道义故而主要讲“义”;而先秦道家、法家重自然法则或社会法则,故而主要讲“理”。一般而言,那些重视人文理想的学者、学派偏重道义(义)的重要性,而重视现实功利的学者、学派则偏重法则(理)的重要性。
对于以典籍知识为职业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写书的目标就是探求和表达“义理”,即确立道义与法则。至于古人留下来的经典,其根本要旨就是承载、传播“义理”。所以,在“义”“理”观念形成的同时,如何从经典中寻求义理就是其读书人的首要目标。《周易》是群经之首,先秦儒者就是希望探求圣人表达的“义理”,故而《周易·说卦传》提出圣人作《易》时,“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颖达《疏》云:“以治理断人伦之正义。”这确是体现出儒家的义理观,即以“正义”的道德价值去“治理”现实的政治秩序。所以,两汉时期确立了儒家经典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后,如何从经典文献中探寻义理就成为儒家经学的使命。这时,与经学相关的概念大量出现,诸如: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王充,第256页)
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王充,第556页)
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唐六典》,第45页)
汉唐时期的儒家经师、学者,以研究经典的文辞章句为业,但他们也意识到,通过经学的训诂章句的研习,旨在“辨明义理”,即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
正由于儒家的“义理”包含着“义”的道义与“理”的法则,所以,尽管“义理之学”的兴起本身是一种学术范式的重要转折,即由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转换成两宋的义理之学,但这种学术范式的发生转换的内在动力、思想根源是复兴儒学的文化功能、政治使命。这种文化功能、社会使命是双重的:一方面要阐发儒学的道义价值内涵,激励儒家士大夫追求“道”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则是要推动儒学治理社会的实用功能,能够指导儒家士大夫在治国平天下活动中建功立业。
二、宋儒义理之学的双重含义
“宋学”所具有的“义理之学”形态,绝不是被许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空谈义理的学说,相反,它从产生就是旨在创建一种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学说。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
从历史事实来看,那种将宋学等同于宋代理学的传统看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两宋时期的学术思潮中,涌现出各种不同的学术主旨的观点与流派,以“道学”“理学”自命的伊洛之学只是诸多学派中的一派,其他还有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等。不仅是这些诸多的学者、学派均活跃于宋代学术思想界,而且他们的学术旨趣、思想观念具有“宋学”的“义理之学”共同特点,就是所谓明体与达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统一的特点。
首先,宋学学者均希望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义理探求,建构一种道德性命之理,以解决世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问题。其实,宋学学者的不同派别均重视义理之学,他们之所以强调经典的义理重于训诂章句,就在于义理能够解决人心世道的价值建设问题。在宋学的义理之学中,“义”的儒家道义价值重振,一直是宋学学者所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推动宋学初兴的范仲淹,即是一位执着于复兴儒家道义价值的士大夫,他们“慎选举,敦教育”,主张“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范仲淹全集》,第237页)。他倡导“举通经有道之士”,在科举中将经义置于章句之上,均是为了整顿士风、重振儒家道义。被称为宋学奠基人的“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均是在宋初主张重振儒家道义的著名学者。胡瑗主张学术、教育应该坚持“有体、有用、有文”,其具体就是“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的儒家伦理、道义的价值信仰;孙复研究《春秋》学以求本义、大义,此“义”也就是仁义礼乐的道义价值,他希望在宋初能够重振儒家道义。石介倡道统论,这个“道”即是儒家推崇的道义价值,所谓“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徂徕石先生文集》,第245页)另外,王安石所创立的荆公新学,同样一直是以复兴“先王之道德”为己任,以重振儒家道义价值作为其学术的根本。他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临川先生文集》,第859页)他主张儒家道义价值的“性命之理”是人心本有的,从而为复兴“先王之道德”确立形而上的前提。与荆公新学同时崛起的洛学、关学等“道学”学派,更是以重振儒家道义价值为己任。他们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相通的义理之学,其目的就是重振儒家伦理,推动仁义礼智信的道义价值建构。如朱熹特别推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书,就在于四书包括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他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朱子全集》,第3640页)由此可见,在宋学学者群体中间,无论是哪一派学者,他们希望复兴三代先圣、先秦儒家道德思想、价值信仰似乎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宋学学者均有很强的经世致用追求,无论是通过经典诠释而建构义理之学,还是直接从历史、现实中探讨经世之学、治世之方,宋学均十分关注并希望最终解决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问题,包括革新政令、抗击外辱、民生日用的治国平天下问题。宋学作为一种纠正汉唐以来“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的学术思潮,他们与那种纯知识化的章句之学有完全不同的学术旨趣,就是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前面所述的那些复兴儒家学说、推崇道义价值的宋学学者,恰恰也是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追求、致力于革新政令事务的士君子。宋学的开拓者范仲淹就是北宋“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他的经义创发、师道推崇、士风重振的道义关怀,其实均是与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选拔人才的经世致用目的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所表达的正是宋学革新政令的经世追求。宋学开创之初的“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创发经义的道义关怀,也是与革新政令的经世追求是一体的。胡瑗强调“明体达用”,其“用”就是“举而措之天下”的经世追求,他在湖州时创“经义”“治事”二斋分科的教学,其“治事”斋要求“治民以安其身,讲武以备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黄宗羲全集》,第56页)孙复的《春秋》大义其实就是基于现实的经世追求,即如欧阳修所说,是“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欧阳修全集》,第458页)在北宋时期,创发经义、革新政令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无疑是王安石。王安石的“经术”与“经世”是统一的,他对神宗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宋史》,第10544页),并由此推动的熙宁变法,来实现他创通经义的目的。应该说熙宁新政是继庆历新政之后一场更加重大的革新政令的运动,充分体现了宋学所具有的强烈经世追求。同样,宋学中其他学派诸如:关学、洛学、闽学等,虽然他们对经义道德、心性修养、形而上思辨方面更加关注,并且更加标榜自己的学说是“内圣之学”“义理之学”,但是他们作为宋学的最重要力量,仍然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经世追求。张载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恰恰是道义情怀与经世追求的统一,他所希望的恰恰是长治久安、太平之世的“三代之治”。二程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只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同,但他们均主张以经术经世务,以治国平天下为学术最终目的。
所以说宋学所追求的“义理之学”,其“义理”的含义正好包括了道义关怀的“义”与治理天下的“理”。几乎所有宋学学者、宋学学派,其实均是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经义与治事、道与治、道义与事功、世道人心与经世致用、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的统一。当然在宋学内部,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与学者,他们除了对经义有不同理解、对政令有不同主张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事功关系上,更加偏重于某一个侧面。在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义理之学”中,究竟是“义”的道义决定“理”的政治治理,还是“理”的政治治理统摄“义”的思想道义?两宋时期最大学派之争,就有北宋王安石新学与二程洛学,还有南宋朱熹的考亭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之争。他们的分歧并不是“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而是道义价值、政治事功两者中谁最根本、更优先。二程、朱熹重道义价值、内圣修养,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道义价值、内圣修养的问题,然后即可实现经世治国、外王事功,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而王安石、陈亮则相反,他们特别强调经世治国、外王事功才是思想道义的前提与目的,道义价值、道德理想最终只能通过治国安邦、外王事功方能得以实现。朱熹和陈亮的学术争辩,就触及这个问题的核心层面。朱熹认为只有三代时期的内圣道德与外王事功才是统一的,秦汉以来尽管出现了汉高祖、唐太宗等杰出的英雄豪杰,能够治国安邦,创造事功,但是他们均无内圣道德。他说:“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都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朱子全书》,第1558页)三代君主皆是由内圣而外王、由道德而事功,故而才是合乎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三代之治。但是陈亮的看法恰恰不一样,他肯定汉祖、唐宗的治国安邦之政治事功的道义价值,他说汉祖、唐宗“终归于禁暴戡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领宏大开廓故也……此儒者之所谓见赤子入井之心也。”(《陈亮集》,第346页)朱熹等理学家坚持道义价值、内圣修养是义理之学的根本,三代王道理想的实现首先就在于诸位圣王坚守了道义的价值与内圣的修养,至于治国安邦、外王事功则只是内圣道德的自然结果。而陈亮则坚持以治国安邦、外王事功作为根本,认为“赤子入井之心”必须依托、呈现在这种治国安邦、外王事功之中。由此可见,尽管朱熹、陈亮均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有体有用之学,均属于义理之学为学术旨趣、学术形态的“宋学”,只是他们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功利方面的不同基点与侧重,从而构成宋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虽然程朱学派在当时及后世被称之为“理学”,其实他们所推崇的“理”主要是道义的价值,故而是“以义为理”;而荆公新学、浙东学派则强调治理国家的功利目标及现实法则,即所谓“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黄宗羲全集》,第56页)他们的义理之学应该是“以理为义”。
三、宋儒义理之学的学术领域
宋学的义理之学追求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故而宋学学者、学派显然不仅仅是宋代理学家、理学学派,而是包括宋代各儒家学者与学派,且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当然是十分多样化的。宋学学者的著作分布在经史子集的不同知识部类中,涉及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文学乃至农、林、医、艺等不同学科。所以,许多学术史叙述将宋学窄化为理气心性的抽象义理,其实不是宋学学者的学术视野狭窄,而是后来学人的学术偏见。在宋学的这些研究领域,均体现了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双重功能要求。
宋学首先体现为对儒家经学诠释的学术创新。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往往将宋学理解为宋代经学,这种理解,其实与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与核心有关。在古代中国,一切思想演变、学术发展、文化转型,均要体现为儒家经学的变革与创新。宋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和重要的学术形态,首先体现为一场经学的变革。正如清学者钱大昕所评述的:“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11页)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王安石、程颢程颐兄弟等均是宋学的开拓者,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各出新意解经”,这一“新意”也就是经学史上反复称谓的“义理之学”。他们特别重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但他们与汉唐诸儒究心于经典的章句训诂不同,而是特别重视对经典的义理探寻。上述的欧阳修、二苏、王安石、二程等宋学开拓者,其实均是以义理解经而获得突出成就者,他们的经学著作,如欧阳修专注“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为古人所未见。”(《欧阳修全集》,第2713页)故而是宋代义理之学的开拓者。王安石也是如此,南宋赵彦卫说:“王荆公《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赵彦卫,第135页)王安石《三经新义》包括对《周官》《尚书》《诗经》三部经典的义理之学。二程亦是以义理解经的大家,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宋学以义理解《周易》的代表作。
宋学不仅通过对传统的“五经”的创发,建立了新的学术范式的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新的经典体系的创建者,他们建立了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中心的新经典体系,并对这四部经典做了系统的诠释,使宋学的哲学观念、政治思想、修身工夫等理学思想与“四书”经典紧密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经过宋学学者的经典建构,中国传统经典体系就不仅有“五经”体系,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甚至地位更高的“四书”体系。
宋学作为一种为强化儒学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文化功能的新兴学术思潮,推动了宋代以义理之学为学术范式的知识建构,最终目的仍然离不开推崇道义价值、经世事功两个方面。首先,宋学强调经典奠定人的道义情怀、价值信仰的根本作用。宋代学人对汉唐经学的不满,首先就在于汉唐学人将经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知识性的章句训诂之学,经典在塑造个体道德心灵、建构社会伦常秩序、奠定价值信仰上的根本宗旨被忽略了。所以,宋学的开拓者将学术重心放在重新诠释经典上,就是希望发挥经学在塑造个体道德心灵、维护社会伦常秩序、重建道德价值信仰上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经典中所阐发的义理,首先就是这种道德及其性命之理,王安石认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王安石全集》,第858页)王安石的“性命之理”的内容和二程所讲是一样的。程颐在阐发《周易》的义理之学就是社会道义价值,他在为《艮卦·象传》作传时说:“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二程集》,第968页)所以,宋学从经典中阐发的“义理之学”,特别强调社会伦理的道义价值。其次,宋学还对经学的经世功能特别追求,他们希望从经典中建构起一种能够对经世治国有实际作用的义理之学,所以,所有宋学学派、学者无不是将经学视为经世致用之学。那些以改革政令、经世治国为主导的范仲淹、王安石、陈亮、叶适通过经典的义理诠释,为现实的政治改革、经世致用服务。同样,那些强调身心修养、道德义理的理学家们,也是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义理经学的目标。如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均为二程理学传人,但是,他们研究经学、建构宋学义理之学的目标就是经世致用。胡安国终生从事《春秋》学研究,著有理学家治《春秋》的代表著作《春秋传》,他主张“《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宋史》,第12913页)而胡宏也强调“学”与“治”是一体的,他说“学者,所以学为治也。讲之熟,则义理明;义理明,则心志定;心志定,则当其职,而行其事无不中节,可以济人利物矣。”(《胡宏集》,第128页)正由于所有宋学学者均强调明体与达用、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故而宋代的经学就是一种将道义价值与功利价值、人格修养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的义理之学。
宋学不仅是指宋代的经学,同时还包括宋代的史学。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陈寅恪集》,第272页),宋代史学的发达繁荣,同样与宋学学者追求的道义价值、经世目的有密切关系。义理之学的价值理想是宋学推动经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同样是他们推动宋代史学繁荣的精神动力。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宋学学者们,往往既是经学家又是史学家;即使有很多学者完全是历史学者,但他们的史学观念仍属于宋学,其从事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仍是宋儒义理之学的价值理想与政治功能。宋代学者热衷史学研究、著有大量史学名著,其动力之一就是探讨历史治乱盛衰的规律,为当代政治人物提供治理社会国家的原则、方法、策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然而从这部著作的书名上看,这部史学著作的目的是供当代朝廷“资治”之用。司马光将历史看作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而其目的则是总结历史治乱兴衰及生民休戚的经验,满足当朝人物的执政需要。他最终编撰成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提供当代朝廷资治的著作。所以,该书很快就得到当朝皇帝神宗的肯定与赞誉,他认为这部书的重大价值就是:“其所以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教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司马光,第29页)司马光这种希望通过史学而探寻治乱之原、提供治国之鉴的想法,在宋代历史学家那里是十分普遍的。那些以理学为主导的学者也是这样,与司马光同时代宋学大家程颐就将史学看作是探讨治乱、安危、兴衰、存亡的学问,他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二程集》,第232页)程颐以义理经学见长,而他的史学观与司马光等历史学家相同,即希望从史学著作中满足当朝执政的需求。另外,那些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宋学学者,亦普遍是这种史学观。如南宋婺学学派吕祖谦以历史文献研究见长,他的史学观同样如此,他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吕祖谦全集》,第218页)可见,吕祖谦以历史文献研究见长,其动机目标也是希望通过史学来探讨治乱之原,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
宋代史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伦理的道义价值的重视。宋代史学探讨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规律时,特别强调儒家伦理之道能够影响、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这样,宋学学者在史学领域特别关注价值与政治的结合。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本来就是德治、仁政,将天下国家的治乱兴衰归之于道义人心。所以,宋儒的史学著作特别强调道义人心对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希望通过写史以对朝廷、百官起到一种劝诫的作用。如北宋唐史名家孙甫的史学观就是如此,他以《尚书》《春秋》为史,认为“《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间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孙甫,第620页)以历史人物的道德善恶来说明政治治乱兴衰,以强调道义的正面价值和历史影响,最后达到对当朝君臣、士大夫的劝诫,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宋儒那明显得到进一步强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特点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第9607页)他明确将历史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与当朝君臣的善恶戒劝结合起来。吕祖谦的婺学偏重史学,与考亭学派以性理见长不同,但其史学仍然将“择善”“儆戒”置之首位。他说“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吕祖谦全集》,第257页)
宋学的学术领域除了经学史学之外,文学亦是一个重要领域。中国传统的“文学”比现在仅仅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的外延更大,它是指以文字、文章及典籍为载体而表达作者的观念、思想、情感的学科,既包括塑造形象,表达情感的艺术类文学,也包括通过思想陈述、逻辑推理以表达思想观念的论说类文章。宋学的兴起,与文学领域的一场重要转型或革命的发生是同步的,即唐宋之间发生的古文运动。宋学的形成和发展是承唐中叶以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发展而来,同样,宋代的古文运动亦是承接唐中叶以来的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而来。韩愈、柳宗元为抵御唐初文学的“六朝淫风”,力倡“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昌黎全集》,第219页)、“文者以明道”(《柳河东全集》,第542页),以复兴儒家之道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北宋时期推动宋代义理之学的领袖人物,恰恰均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可见复兴原始儒学的宋学思潮,是推动古文运动的根本力量。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文坛出现“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的局面。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如王禹偁、穆修、范仲淹、孙复、石介、欧阳修、苏轼等重倡“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古文运动,以复兴儒家之道。其实,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追求,与宋儒所追求的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义理之学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主张,以新文体取代旧文体,其新文体包含的“道”恰恰体现为道义关怀与经世追求、内资修德与外济经世的统一,正是宋学所追求的学术精神。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子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欧阳修全集》,第978页)无论是学者学术追求的“道”,还是文章所要表达的道,均是必须能够“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明体达用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其实,这一观念,恰恰是宋代的学者文人的共识。譬如胡瑗主张为文、为学均得“以体用为本”,他坚持“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全集》,第25页)他认为一切文所载之“道”就是这种“仁义礼乐”的道义信仰与“措之天下”的经世之具。石介推崇的“文”也是如此:“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徂徕石先生文集》,第135页)“教化仁义”是明体之事、内圣之德,“礼乐刑政”是达用之功、外王之业,但均要通过文辞而表达、传播。又如李觏也认为,“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李觏集》,第288页)他推崇的这种“文”,也是包含着全体大用、内圣外王之道。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论宋代理学与新学的关系
——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
⊙蔡方鹿 李琛
宋代理学代表人物二程朱熹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宇宙观,以性善论为主的人性论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及与之相关的存理去欲的理欲观。理学由重义轻利和提倡道德自律而表现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则提出以元气为道之体的道本论宇宙观[1],“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2]的人性论,趋舍唯利害,“义固所为利”[3]的义利观。新学由重视事功和社会治理而表现出重外王的倾向。
理学与新学在宇宙观、人性论、义利观以及治国理政观念上的差异引起了双方的相互批评。但二者又同属重义理的宋学,又相互影响和沟通。理学的完善与确立,直接受益于新学。新学和理学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大发展。双方地位的消长,直接影响了后世学术与政治的发展进程。虽然新学在南宋时逐步失去了其在北宋时形成的官学地位,后又渐趋沉寂,但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本文就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异同互动关系,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再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理学与新学的相近处
理学与新学在宇宙观、人性论、义利观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治国理政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由此展现出两派思想各自的特点。理学重义轻利,主张节制统治者和人们的欲望以维护社会稳定,并通过存理去欲以恢复先天的善性,所以讲性善论。而王安石新学则在价值观上重视功利,发展了儒学中的“外王”部分,并将其义利观付诸实践,以义理财,推动新法改革的实施。因此,新学的义利观既是改革的理论需要,也是新法的理论基础。王安石强调:“世无常势,趋舍唯利害。”[4]他认为人们的进退、行为举止以趋利避害为原则,表现出对客观利害的重视。并认为取利、有用是天道自然的原则:“盖有常以为利,无常以为用者,天之道也。”[5]强调利是有常,用是无常,均为天之道,肯定利的用处和价值乃普遍的规律。在人性论上重视情,认为“性生乎情”,有了情才有善恶,不认同性善论。由此形成理学与新学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主要是价值观和人性论上的分歧。
以往学界对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差异论述较为充分,而对理学与新学存在着的相近之处则关注不够。以下着重探讨二者在同属宋学而批评汉学,既重视功利又重视道义,以及在尊王黜霸等方面的沟通与相近之处。
(一)同属于宋学而批评汉学
理学与新学都属于宋学,重视阐发义理,批评汉学单纯重考证训诂的学风。二程站在宋学的立场,主张道理可不受解释文义的约束,指出:“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6]把阐发道理放在首位,即使文义解错也无碍。程颐由此批评了只重文字训诂而不及道的学风:“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7]把经典作为载道的工具,指出只对经典文字加以训诂而不求道,不过是无用之学。朱熹继承二程,对汉儒偏重训诂而忽视义理的学风提出批评:“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8]以上程朱对汉学的批评,反映出汉宋学之别在于重训诂还是重义理。
新学作为宋学的重要派别,亦对汉学学风提出批评,这是其与理学家的一致之处。王安石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9]强调治经学以致用为目的,“学者不习无用之言”,这体现了王安石新学与汉学的差异。
这里王安石和程颐均把章句训诂视为“无用”之学,这是二者的相同处,共同体现了宋学通经致用的学风。王安石指出:“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10]其对汉学的批评成为理学的同调。正如李存山先生所指出:“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批评科举考试,‘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新义》颁布于学官,至此,‘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李存山)认为王安石新学批评汉学崇尚章句文辞之病,并颁行《三经新义》,以宋学取代汉儒之学,是因为受到范仲淹的影响可溯源于庆历新政。新学的这一思想与当时理学家批评汉学的倾向是一致的,而同属于宋学。
(二)理学家亦有重视功利而与新学相近的一面
以往认为,理学家重义轻利,与新学重视功利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故在变法指导思想上出现对立,分为各自不同的派别。这种认识虽有道理,但还须进一步探究。新学对客观事功和利益的重视不言而喻,然而理学家也并非只讲义理不讲功利,亦具有与新学的相近处。
二程重视义利之辨。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11]]认为天下之事都可用义利标准加以衡量。他认为不得抹煞利的存在,而应肯定利的作用。程颐说:“‘故者以利为本’,故是本如此也,才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顺,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112在解释“故者以利为本”时,程颐充分肯定利原本就具有的价值,而不是排斥利。认为利的存在,与性密切相关,不利则会害性。如果人无利,便失去了人生存的条件。因此承认“天下只是一个利”。但对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利的进一步追求,程颐表示要加以控制,以防止“趋利之弊”。二程更多地强调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利,认为“水利之兴,屯田之制,府兵之复,义仓之设,皆济世之大利”[13。这体现了二程对功利的重视。
朱熹在重视道义的同时,亦重视功利,提倡义利统一而不空谈道义。他说:“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14所谓“义未尝不利”,便是义利统一,在讲道义之时,利也在其中。并强调讲道义是为了求利。“义有大利存焉”,义之中就有大利,义不能脱离利而存在。这表明义利共存,不可分离。并继承二程的义利观,指出:“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15]朱熹在引用二程“君子未尝不欲利”的观点时加以发挥,认为专门讲利则有害,而以仁义为指导,即使不去求利,也会带来客观的物质利益。可见理学家并不排斥功利,而且在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程颢、朱熹、张縂、吕祖谦等著名理学家关心民众疾苦,视民如伤,在各自的任内做出不少有利于民生的实事。这表明,理学对于功利并不是排斥的,而是把功利包含在道义和义理之内而加以重视。这与新学有相似之处。
(三)新学亦有重视道义而与理学相近的倾向
以往认为,新学重视功利,理学重视仁义,在变法指导思想上形成对立而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对峙,并影响了两宋时期思想学术与政治的演变。但新的研究表明,新学在重视功利的同时,亦有重视道义的倾向,这与理学相近。如王安石指出:“彼区区聚敛之臣,务以求利为功,而不知与之为取,上之人,亦当断以义,岂可以人人合其私说,然后行哉?”[16]王安石主张把功利与义结合起来,使功利符合义的原则,并不完全只重功利。他还指出:“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17王安石在重视功利、经营天下财富的同时,更重视道义的指导,强调理财不可无义。尽管需通过理财来满足天下人的财货需求,但王安石主张理天下之财不可脱离义的指导,表现出义利结合的倾向。
熙宁变法期间,当神宗询问制置条例的新法制定如何时,王安石向神宗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118]指出治国理政应有先后缓急,如果强调理财,就会重视“使能”,而将“任贤”置之于后,造成朝廷只务理财,而对礼义教化未有顾及,以至于带来风俗弊坏的消极后果。所以王安石认为还是应以礼义教化为治国之先。可见新学在实施变法时,也是主张任贤,重视教化的,而且对理财加以一定的规范,在理财的同时不放弃“礼义教化”之道义。
进而,王安石把理财本身就看作义。他说:“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19]指出政事是为了理财,理财乃为民的公义。王安石对利加以解释,把利界定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认为周公作《周礼》,重视理财,提倡为民之利。可见礼义、道义与利不可分。他还主张公私兼得:“故市不役贾,野不役农,而公私各得其所。”20]提出公私结合,而不是排除私人之利。并作诗以肯定“道义”:“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21]这表现出王安石重视道义,并一定程度地肯定孟子和韩愈的思想倾向。
(四)双方都重视尊王黜霸,批评霸道政治
战国时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反对霸道,提倡王道;主张行仁政,以仁义治天下。王道即尧舜、三代先王之道。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22]霸道是指凭借武力假借仁义以征服别人。“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3]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认为春秋五霸行霸道,与王道相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24]即齐桓公、晋文公等是夏禹、商汤、周文武王的罪人。后来荀子主张王霸不偏废,“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25]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认为儒家王道已过时:“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6]强调与以力相争的时代相适应的只能是霸道,如果不行霸王之道,只会带来乱世。“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27]并指出,儒家的仁义不足以治国,尧舜之道也不能为治,称赞被孟子批评的齐桓公:“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8]表现出法家的霸道与孟子王道思想的对立。
秦汉以后王霸并用,霸王道杂之。至宋代,关于王霸之辩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
程颢指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炫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29]把王道加进了天理的内涵,体现出其时代性。程颢既批评假借仁义以行霸者之事,又批评以霸者之心来求王道。指出孔子后学之所以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曾耻于与管仲为伍,是因为“义所不由”,即推行霸道,违背了仁义的原则。表现出程颢在新形势下尊王黜霸的思想。朱熹继承孟子、二程,讲王霸之辩。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齐桓、晋文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设使侥幸于一时,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则固霸者之道也。故汉宣帝自言汉家杂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30]朱熹指出王者之道是致诚心以顺天理,使天下服。而霸者之道乃假仁义以济私欲,如春秋五霸之齐桓、晋文。在朱熹看来,王霸之辩在于是否顺天理或假仁义,即以义利、公私、理欲作为划分王霸的标准。
尽管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重视功利和外王,在变法中积极推行各项社会改革措施,但他对王道政治仍表示认同,并批评霸道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的尊王黜霸思想。他说: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何也?盖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其功异则其名不得不异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为也,唯恐民之不见,而天下之不闻也。故曰:其心异也。[31]
王安石论王霸之别,认为其用相同,表面上都讲仁义礼信,但其心则不同,王者之道认为仁义礼信是原本应当为的,所以以仁义礼信修其身,并移之于政治,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无不化。但霸者之道则不同,其心并不在仁,只是担心天下人恶其不仁,所以表面上也讲仁;其心也不在义,只是担心天下人恶其不义,于是表面上示之以义。对于礼信也是这样。所以说霸者之心是为了追求利,而假借王者之道以求其所欲。这表明在王安石看来,王者和霸者,其思想实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此而言,王安石区分王、霸的目的,是批评霸道政治,主张实行仁义礼信之王道政治。这与程朱等理学家批判的假借仁义而行霸道的王霸之辨有类似之处,亦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
二、新学对理学的影响
由五经训诂之学转向为四书义理之学,体现了由汉学向宋学的时代转型,这与王安石新学对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四书义理之学伴随着宋代《孟子》的由子入经而逐步形成。虽然二程在唐代韩愈、李翱开重视四书之先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孟子》等四书的地位,但二程的影响力有限。而王安石在当时则身居高位,领导变法,直接对科举进行改革,使四书这种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得到官方的认可,更把《孟子》《论语》规定为官学教材,为《孟子》的由子入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理学家难以相比的。
在上述方面,新学对也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王安石倡导义理和道德性命之说,批评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与理学的学术旨趣相近,而且王安石在主持当时的熙宁变法中直接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规定不用注疏,务通义理,更把《孟子》等定为兼经,完成了把《孟子》上升为经书的过程。中书言:“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32]在废除以诗赋取士的同时,规定以《论语》《孟子》为兼经,这为四书系统的形成和四书义理之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务通义理”的宋学逐渐替代了重视训诂考据的汉唐注疏之学,并为宋学之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马端临指出:“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则于学者不为无补。”[33]所谓“变声律为议论”,即指以己意说经的议论之学代替讲究语言声调韵律的诗赋之学;而“变墨义为大义”,即是以义理代替记诵,认为王安石这种对科考的改革,有补于学者。又颁行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于全国。“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34]汉唐传注之学废而不用,使得对整个儒家经典的诠释之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转折。王应麟对此加以评价:“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35]王安石新学的兴起以《三经新义》为文本,以讲义理为重,成为汉儒训诂之学被宋代义理之学所取代的重要表现。这对宋学之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理学与新学在同属宋学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新学亦遭到了程朱等理学人物的批评,但新学和理学都属于宋学,共同批评汉唐章句训诂注疏之学,而重视和提倡义理,这即是双方的相近处。如宋代易学之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颐,以义理解释《周易》,就要求学者看王安石解《易》的文字。他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36]程颐提出,学者欲治易学,就须看王安石的《易解》等义理易学的文字,因为他们都属于易学的义理学派,都对汉易之象数学进行了批评。这反映了新学与理学在提倡宋学义理,批评汉学方面,具有共同之处。
从以上看,在经典文本上,新学与理学均重视“四书”之《孟子》,尤其是王安石改革科考,规定将《孟子》等列为兼经,成为科举考试必考之经书;不须尽用注疏,从制度上为兴起宋学及“四书”义理之学提供了保障。四书学的形成,尤其是《孟子》得列经书,王安石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大于诸理学家,亦是理学家所不可替代的。另外在对《周易》的解析上,程颐要求学者读王安石的解易文字,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新学对理学的影响;以宋儒义理之学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双方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理学受新学影响而互动的原因。
三、理学与新学的消长、辩难互动之启示
通过宋代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使得在两宋时期前后延续近百年之久的新学与理学之争,从整体上以新学的失势而告终。以杨时、胡宏、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新学的批评及政治上的原因令新学逐步丧失了其官学地位,而理学则在南宋后期成为官学,这种批判促使思想文化风向发生转变以及官方学术产生更替,使得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此至元明以降,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否定之说遂成定论,理学则一枝独秀。
理学与新学的异同、新学对理学的影响、理学对新学的批判,客观反映了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人们既要看到理学与新学对立相争的一面,同时也应看到二者相互影响、沟通融合而促进宋学乃至理学发展的一面。
理学与新学的消长、对立互动主要表现为在北宋时新学居于官学地位,理学此时属于宋学的重要一派,在与新学等各派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发展。二者相比较,新学可谓是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并用,内圣与外王同倡,但对经世致用和外王更加关注;理学则在不偏废经世致用与道德性命、内圣与外王的同时,对道德性命和内圣更为重视。这与双方的学派性和特质相关。理学虽一度遭统治者废黜、禁止,但在南宋后期逐渐占据了官学地位。新学与理学消长、辩难互动带给人们的启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任何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都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合
新学和理学都曾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了宋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都曾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其思想理论也引起变化。
新学是“熙宁变法”的理论指导。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与变法相适应并为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是王安石提出的以《三经新义》为载体的新学思想,及在其他著述中阐发的新学理论。这基本适应了当时社会要求变革的需要,是新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新学在北宋时曾独尊于世,但由于北宋亡国,进入南宋后逐渐成为众多儒学批判攻击的对象,以致著述散佚,几乎处于湮没无闻状态。与此相反,理学虽在北宋时尚无很大的影响力,但至南宋其影响却处于不断提升中。由于理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基本适应,是针对汉唐注疏之学的流弊和佛教盛行冲击儒学的回应,是为了解决因旧日儒学发展停滞而带来理论危机并造成社会危机等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理学与新学理论的提出及其际遇,与其学派及其理论是否适应宋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密切相关。
(二)义利兼顾,情性相容
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虽有对立相争的一面,也有渗透融合、相互影响的一面,并非完全不相容。尽管新学重功利,理学重义轻利;新学讲善恶非性而在情,理学讲性善论,二者具有明显差异,但亦存在着融通相近的一面。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应重视二者相互影响、沟通融合的一面,树立义利兼顾、情性相容的观念,而克服各自理论的局限和偏差,以促进学术思想理论的完善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内圣外王,兼容并收
两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关系之所以表现出消长更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学与理学因其学术内在根基的差异,而对圣人之道与儒者修身的取舍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继而在“外王”与“内圣”的取舍问题上有着不同见解,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学重外王而兴起事功,理学则重内圣而坚持修身。对此,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37]二程偏重于义理心性之学的探索,并坚持内省的修养工夫,这也是宋学之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王安石则更为注重外在功效,他在与宋神宗的对话中曾语:“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38]执掌政权的王安石站在治理国家的角度,以通经致用的“外王”之道实践儒家先王经纬天下之意,其意本在救国利民,这放在北宋多灾多难的危急时刻原本也无可厚非。面对二者不同的态度,我们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双方各自的不同立场及不同思想理论的分歧,不能武断地认定孰是孰非。但对于内圣或外王某一方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另一方,都会带来一定的偏颇和流弊。儒家讲求修身成圣,并贯彻到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中,即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德才兼备。这无疑是十分全面的。
理学与新学之间在义利观上的差异和互动融合产生的结果是重义轻利的观念逐步占据了上风,但也不排斥对功利和客观物质利益的重视。理学由其重义轻利和提倡道德自律的特质而表现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新学由重视事功和社会治理而表现出重视外王的倾向,经理学与新学的互动而表现出义与利、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的倾向。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应将内圣与外王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兼容并收,而避免单纯重内轻外或只讲外在事功,不讲道德自律的片面性。我们探讨两宋时期理学与新学的相互关系,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克服两者的偏颇和片面之处,而吸取它们的长处,并将其结合起来而纠其偏,使其发挥应有的启示作用。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至今仍值得人们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借鉴。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朱人求
话语是关于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是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语言或文本而展开的社会交往与关系建构的实践。话语是哲学的表现形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话语,时代话语的转变往往意味着社会思潮的变换。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话语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是指对话语的语境、语义、语法、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性回顾与展望、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亲和性、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拓展、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操作等问题的追问与阐释,我认为,话语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将带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回顾
中国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它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说它年轻,它是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新学科。所谓范式转换,它指一种研究模式的根本改变,库恩把范式的转换理解为概念图式的更换,即“更换思维的帽子”[2]。回顾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西学范式和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率先提出中国哲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先秦时期群星灿烂,诸子百家蜂起,迎来了中国哲学最辉煌的子学时代。面对思想的失范和价值危机,诸子百家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共同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轴心时代”。西汉时期,汉武帝雄才大略,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哲学步入儒学独尊的“经学时代”,儒学也沦落为一种统治术,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哲学。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基本可以区分为子学范式和经学范式。[3]
所谓经学范式,是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各家各派恪守经典文化传统,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考订,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不敢阐释自我,追求经典阐释的客观性和承传性,中国哲学史上的汉学传统就是古文经学研究范式的最佳范例。所谓子学范式,是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各家各派立足时代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和思想阐释,追求思想的时代性和原创性,中国哲学史上的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子学范式的杰出代表,宋明理学中的宋学传统较为接近子学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经学范式与子学范式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子学中有经学,经学中有子学。当某一研究范式中思想的时代性和独创性胜出的时候,我们通常视之为子学,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就被认为是子学范式,而把那种追求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考订、注重经典的权威性和历史性的学问视之为经学,其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就是经学范式。
(二)西学范式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接纳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但未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这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19年和1934年出版,后者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框架和典范。概而言之,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采用西洋思路与形式,拿西洋哲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自来学者的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西学研究范式。
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五步法[4])和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此为指导,借鉴西方近代哲学的书写范式,胡适建立了以“明变”“求因”“评判”为内容的哲学阐释框架。所谓“明变”,就是考察各家哲学思想渊源、相互影响及其变化的线索;“求因”,就是探索各家哲学思想兴衰变革的原因;“评判”,就是根据各家学说的影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就这样,通过纵向的渊源、流变的贯穿与横向的以哲人或每一个学派为中心的扩展,胡适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率先建构了一个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史阐释系统。在表现形式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明确区分了哲学与经学的疆界,对先秦诸子给予同样的地位;与经学的注释形式针锋相对,胡适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以经典的原文作为自己的注脚,中国哲学史彻底颠覆了经学范式而步入西学范式,从而获得了现代学科身份。《中国哲学史》尽管只完成了上卷,但是它完成旧有哲学史写作方式的解构,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制的先驱。
在严格的意义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坚信,中国古代哲学尽管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性,但有实质的系统,因此有必要运用逻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新梳理,“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5]他还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其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这种建构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选出类似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将这些内容重新组织起来,遂成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整个一生的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做这项精挑细选的工作,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中国哲学史的主要人物、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在这三部哲学史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演绎。冯友兰还提出了遴选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基本标准:属上述哲学范围者、有新见且有自己系统者、有中心观念者,以及可作辅助材料的杂家之书,哲学家之人格、气质及思想社会背景均可作为哲学史史料。通过这种系统的整理与建构,中国哲学史旧貌换新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将中国哲学史纳入经济社会史解释框架中,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研究范式的构建。侯氏把胡、冯作为对手,认为胡、冯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然而,中世纪思想家研究,必须着重考察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7]侯外庐将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话明白地概括起来,就是: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和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来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8]侯外庐带着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进入学术领域,他所概括的是一个后来在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派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基本上没超出其框架。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倾向于将一种简单心物二元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解释原则和主要发展线索,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的历史,有失于简单化之嫌疑。
西学范式一统天下,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十分突出。金岳霖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像是一位美国商人写的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存在较大的隔膜感。冯友兰的“有似论”研究范式,则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9颜炳罡则认为,这种西学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砍掉了中国哲学的原典时代,使诸子之学成为无源之水;其二,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分解、打碎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整体性,使中国哲学由有机整体变成支离破碎的材料;其三,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集体失忆。简单地说,就是斩头,肢解,主体性丧失。[l0]如何走出西学范式,寻找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哲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三)多元化发展趋势
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统天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重写思想史、重写学术史的思潮。具体到中国哲学史研究,解释学、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大行其道,一方面这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也落入了西学研究范式的窠臼,因为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史有一件大事就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的问世。葛兆光指出,以往的哲学史都是围绕精英和经典写作“正统”思想的哲学史,这是哲学史很难改变的思路和方法。在冯友兰那里,就是以孔子和儒家、理学为历史线索,因为那些“非正统”的也就是非精英和非经典的东西里面,在冯友兰看来,确实很少有能够称得上“哲学”的东西。尽管后来我们中国的哲学史已经放宽了尺度,降低了门槛,但是,至今的哲学史叙述仍然是精英和经典为中心的,仍然在西洋哲学的尺寸和范围内,“抽取”和“选择”符合“哲学”的资料来叙述。但是,在古代历史和社会里,真正成为指导政治和生活的那些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中,还有很多不能被“哲学史”所描述的、一些“非正统”的东西,它们常常逃逸在哲学史的书写之外,那么,我们是否要用比较宽泛的、更有包容性的思想史来叙述呢?而那些导致思想与信仰发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与思想相关的社会生活史,是否也需要思想史来描述呢?因为思想史首先是历史,那种历史的场景、语境和心情,是思想理解的重要背景,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思想史是人们的观念与感受的历史”,“观念”可能可以被哲学史容纳,但“感受”就不仅仅是精英的和经典的,也包括一般民众的,不仅仅是理智思考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气氛构成的思想背景。[11]
21世纪伊始,学术界热衷于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家都普遍期望的中国哲学能说汉语、能“自己说自己”,走向多元、回归本土的研究范式,充其量还只是“哲学在中国”,还算不上“中国的哲学”,更没有形成标志性的成果和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需要一种“范式”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更多体现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不仅国内的研究深受现代主义思维范式的影响,而且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也不例外。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传统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解读中国古代哲学,例如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冯友兰的新实在论、贺麟的新黑格尔主义、牟宗三的康德哲学、唐君毅的黑格尔哲学等。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都表明了我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依然没有上升到一种范式建构的自觉,中国哲学研究亟须完成“范式的转换”。如果没有这种“范式的转换”,将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导致远离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也就是说以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必然遮蔽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限制了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开放性理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埋没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独特和固有的东西。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学者用一种现代主义的模式来解读中国古代哲学,以削中国古代哲学之足适传统西方哲学之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范式的转换”,那么也将会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与时代精神脱节,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不能反映时代的精神,不能体现时代发展最新的趋势和需要。中国哲学如何回归中国,中国哲学如何接地气,如何接续上时代的脉搏,我认为,广泛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哲学话语势在必行。
二、话语分析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语法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第一次使用“话语分析”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他于1952年发表了“Discourse Analysis”一文,这篇论文通常被认为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话语分析的广泛应用于多种学科。这一时期,话语分析长足发展的标志就是两本杂志——《话语过程》和《语篇》,从此,“话语分析”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代表性学说有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尤其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代表。21世纪以来,话语分析研究仍在横向发展,即向着各个学科渗透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话语。
话语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但西方哲学界却对此持谨慎态度,以话语分析方法来分析哲学话语的成果相对较少。[12][就国内而言,目前仅见陈来先生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和几篇论文,陈来先生的论文对宋明理学话语的形成、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中对道学“中和”说、“穷理”说,对朱子的《仁说》、心说、道体说,陈淳的《北溪字义》,张栻的《太极解》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3],开始摆脱传统的以范畴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海外,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较早将“话语”理论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学研究。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他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作为思想学术事件,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14]艾尔曼把从理学到朴学的转换既看作一种儒学范式的转换,也视为一种儒学话语的转换——一种“从道德主义话语转向知识主义话语”“追求客观性的思潮压倒内圣理想”的革命。可见,话语的转换带来社会文化思潮的转换,也带来了儒学话语的变革。
基于话语分析方法的特质,我认为,话语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二者之间存在着亲和性。首先,话语源于日常生活世界,话语本身也指向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国哲学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强调认知与行动的一致性,恰好与话语分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其次,与儒家哲学立场相类似,话语分析非常重视话语与历史、现实生活的关联。“话语分析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对一个话语链或一团相互交织的话语链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或与现实相联系来分析;同时还应做到对话语链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做一些谨慎的说明。”[115中国哲学话语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是话语链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历史、现实不断交涉的过程。第三,注重哲学话语的具体语境的剖析。由于中国哲学话语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我们只有把哲学概念和范畴放进特定的时代和生活境遇中进行分析,才能诠释出其中沉默的“微言”和“大义”,才能达到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内在精神的真正把握。在这一点上,话语分析方法无疑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灵活性。
话语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实践,将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突破。范式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成熟的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方法、问题领域、解决问题标准的源泉,获得范式是这个领域成熟的标志。范式转换指知觉上的“格式塔[16]转换”,即抛弃原有的概念图式,抛弃概念本身进入到话语领域。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需要改变原有的以西学为主导的宰制性话语模式,由中国哲学自身话语完成自己的系统建构。具体而言,新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将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如下新的突破。
(一)从理论到实践
话语比范畴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为的关系往往比范畴、概念更直接。在社会行动中,话语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象(在心里预演或计划)或事后被理解。因此,有不少话语可以说是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James Paul Gee指出,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离不开社会活动。同样,没有社会活动也就没有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社会活动可产生和改变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因此,话语分析有必要研究人们如何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来进行社会活动、建立社会身份(identity)。[17]话语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反映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话语能对社会进行构建。话语具有建构知识和社会的能力,话语能建构物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建构活动,建构政治,建构身份关系,建构联系和符号系统等。
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和过程。“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准确地说明这个被称为话语实践的东西。……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而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8]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体现着权力和意识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既能促进社会再生,也能促进社会转型。NormanFairclough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分析则必须是一种多向度的分析方法,即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应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实践、一个话语实践和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19]
以“定性”话语的展开为例,“定性”是宋代道学的一个重要话题。针对张载因日常生活中外物的干扰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而发出的疑问,明道的精彩解答成就了一个经典学说——“定性说”。明道的“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绝非纯粹理论指导,它直接指向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何展开行动,或者说,认知的落实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朱子强调“存养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要有“存养”,要“功至”而后才有“得”,“得”的前提就是行动,它不指示纯粹的认知。西山讲“体”不离“用”,讲“以道养心”“以理养心”,对“用”和“养”的重视也是如此。简言之,道来自“伦常日用之中”,知“道”的目的是践“道”、行“道”,这正是儒家哲学的一贯立场。[20]同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仿,话语分析不仅仅是理论分析,它指向社会实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21]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22]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对概念、范畴的重视远远高于对实践的关注,有的甚至完全把实践排斥在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但话语实践一旦进入哲学关怀的视域,我们的哲学研究关注的不再是静态的思想观念,而是动态的话语实践及其历史发展进程。
(二)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话语就像“由‘社会知识库藏’连接而成的穿越时间的河流”,它从过去走向未来,它圈定了现在,并且以另外的形式继续流向未来![23]定性话语一旦奠定,它也由现在走向未来。话语分析也从传统哲学注重结论的静态分析转换为注重过程的动态分析,注重话语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把话语分析概念比喻为“采石场”,意思是说各学科皆可以从中提取原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这些材料是零碎的、无系统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把对知识和话语的考察比喻为思想考古,通过对知识和话语的深层历史的发掘,在现存的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的因子,从而揭示出被我们所忽视的珍贵的历史线索。简言之,福柯的知识考古的目的在于揭示出知识的先在结构,然后对话语的产生与发展、类型与规律等展开深入的分析。
明道的《定性书》是宋明理学的经典文本,它提出的“定性”话语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定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演化版本,并提出了许多远远超出本文意义的思想命题,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从主题上看,话语链是一个整体性的话语流程,它由一系列的话语片断构成。一般来说,思想的发展演进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通过对某一话语链的不断展开诠释、不断补充、丰富和深化其话语片断来完成的。从明道的《定性书》到朱子的《定性说》到西山的“定性论”,“定性”话语经历了一个由工夫论到效果论再到本体论的不断深化发展过程,显示出宋代“定性说”内在的发展理路。“定性”话语也由原来的性与情、性与心、动与静、定的工夫等话语片断逐渐扩展为“仁立义行而性定、理定于中、理即事、事即理”等话语,形成一个独特的整体性的话语流程。朱子和西山的创造性诠释,则体现了诠释的主体性、时代性、创造性和独立精神,体现了话语研究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为后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点和预设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当然,话语的诠释也与诠释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和人生体验密切相关。理解既是个体的行为,又是时代的行为。最后,当我们谋求某一问题的未来发展时,还必须注意当前话语链中主要话语的改变及其与其他话语链之间的相互关系。话语主题的转向也标志着社会思潮的转变。我们看到,当“定性”话语中的主题——“性”被置换为“心”时,“定性”话语的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定性”学说也完成了与心学主题的转换,它也意味着道学思潮开始向心学思潮的转变。
(三)话语与语境
话语分析特别注意话语语境分析,不同的话语在特定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James Paul Gee指出,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离不开社会活动。Gee非常重视结构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认知分析法,尤其强调语境的作用。其中,社会文化分析法把话语当作交际动作来分析,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由于语言交际涉及各种社会文化语境,我们不能单靠语言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来决定其意义,还要参照话语以及话语所产生的语境。话语和语境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话语受到语境的影响,同时也在影响、建立或改变语境。[24在相同的社会情境下,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社会文化知识的使用不同,话语也不一样。同一个社会文化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遵循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交际规则,交际才成为可能。
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25]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定性说”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透过明道、朱子和西山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道学家们对释老学说的排拒,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微言大义”的传统。当张载向明道请教“面对外物的诱惑如何保持不动心”时,明道的回答建构了一种师生的关系。朱子与学生的解读与问难既有思想家的成分也有师生的成分。西山则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把“定性”话语系统与帝王之学结合起来,在《大学衍义》中,“以道养心”“以理养心”的“定性”工夫直接指向的是帝王的修为,于是乎,一个在原初意义上仅仅指涉内在的身心修炼“定性”工夫也获得了外王的权力。
(四)从同一性到差异性、从连续性到断裂性
“话语分析”的主流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倾向,因而话语分析具有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注重差异性和断裂性的特质。话语分析把一切思想理论都平等地视为论述或陈述(一套说辞),把一切对象都一律地视为处于特殊语境之中的特定话语或带有特定价值预设即主观性的“陈述整体”,从而否定话语的确定性和真理性,从而否定真理的权威(其极端者如拉康(Jacques Lacan)干脆声言“真理来自误认”)。与确定性追求相比较,话语分析更为强调话语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建构性,重视揭露话语主体的言说或分析策略、政治动机、价值预设及其实践功能,致力于追究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传播和运作的社会化过程、作用方式和形态等,拒绝进行延续性的探索和原有思想史常用的那种影响分析,表现出一种对断裂和离散的偏执。福柯非常自觉地将他的“话语实践”即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加以区别。在他看来,传统思想史总是致力于在它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求“内聚力的原则”、共同点和一致性,最终总把矛盾消解在某种同一性之中,而话语分析则以描述、再现矛盾和差异本身为使命,它“描述各种有争议的空间”“不试图在矛盾中发现共同的形式或者主题,而是试图确定它们间离的尺度和形式”。[26其实,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绝对漠视连续性,在话语构型(discourseformation)中某些连续性他是不得不承认的。不过在分析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他更关注话语的断裂、强调历史的歧路和岔口,挑战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预定论和目的论。对影响、传统、进化、因果和发展这些传统中心概念的使用,福柯始终保持着警惕和反省。
当我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时,出于不同情境之中的同一话语往往具有不同的思想史意义。当程朱陆王在对“心”“理”“性”“命”“知”“行”等基本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话语片段)展开辩论时,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文本和境遇中它们的含义不尽相同,往往会陷入“鸡对鸭讲”的盲区。还是以“定性”话语为例,明道、朱子和西山有关定性的分析分别代表工夫论、效果论和本体论三种不同的理论类型,三位思想家以自己的独特理解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定性话语系统。如果是程朱理学一系对定性话语的理解有其内在的一贯性,那么,阳明心学对定性话语的界定则是断裂性大于连续性,从而完成了定性话语从理学到心学的创造性转换。
(五)从你—它到你—我
对话主义,顾名思义,即一种与述谓性的“独白”原则相对立的、而以交谈性的“对话”为宗旨的学说与思想。布伯对话主义哲学的思想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用我与你取向取代我与它取向。在传统西方哲学里,哲学研究的对象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我—它关系为其基本取向的。所谓我—它关系,即主体之于客体的关系。布伯则从我—它关系转向我—你关系。所谓我—你关系,即主体之于主体的关系。它不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会合”“相遇”关系,我不是把一切存在物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或伙伴性存在。第二,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在传统西方哲学里,立足于我—它取向的理论必然使一种主从性的原则作为其指南。它们或像古希腊宇宙本体论那样坚持“它”是支配者,“我”是从属者;或像近代康德理性本体论那样坚持“我”是支配者,“它”是从属者。与这类“父子型”的“还原论”或“基础主义”的哲学完全不同,布伯则坚持“关系是相互的”,关系双方并无主次、等级之分。第三,用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在传统西方哲学里,为跨越“我”与非我的“它”之间的鸿沟,哲学家往往诉诸和求助于某种中介性或媒介性的手段的建立。布伯则从间接关系走向直接关系,积极维护人与对象之间的非人为的天然联系。[27]
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一种求知(真理)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则是求道(至善)的哲学。“道”就是说话,就是对话。因而,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时,我们发现,这种对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早已出现。中国哲学有天之道,也有人之道,天地人为三才,三者相互沟通、相互对话。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古与今之间都在密切地对话,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成为中国哲学永恒的追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哲人之所以一开始就把“道”而非“理”作为其哲学的终极关怀,这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哲学的对话主义实质的最集中体现。中国哲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宋明理学又称道学,道是其最高的哲学范畴。在宋明理学中,道既是本体之道,也是道统之道、言说之道。宋明理学家都有自己的语录,通过对话来完成教学,通过对话来完成思想的建构与表达。在言说之中,你与我是对等的、当下的、直接的,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是交互的、同时性的,充分体现了对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人道与天道的对话与沟通中,理学家强调“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等,儒家的“仁学”成为沟通天人万物的中介,成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人伦的最高道德,它无所不包,生化万物,这样一种“仁道”充分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对话精神,通过“仁”的作用,每个人都不断消除小我、不断扩充大我,以同情心、同理心与他者对话与沟通,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实现天人一体,天人合一。
(六)从范畴、概念分析到话语(语句、语篇)分析,注重文本分析
尽管话语分析已趋向于避开对抽象或理想化结构的研究,笔者却认为,话语分析相对于曾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广泛流行的“范畴体系”研究仍有它的优先性。陈来先生指出,范畴体系研究“可以在范畴系统的一般特征方面显现出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不同,但范畴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具体问题的讨论,不是从具体的哲学讨论中理解范畴概念的意义,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的、笼统的说法上,而无法真正促进我们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具体讨论的理解。”[28]这里的“具体问题”即“具体语境”,对哲学话语的理解离不开它的具体语境,只有把哲学概念和范畴放进特定的时代和生活境遇中进行分析,深入研读文本,诠释出其中沉默的“微言”和“大义”,我们才能达到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内在精神的真正把握。中国话语分析应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由概念范畴的静态性分析走向动态性研究,注意话语与社会建构、话语与社会行动之间的有效关联,注重实践性、时间性、对话性、当下性是中国话语分析最为独特的地方。
道学话语分析打破了原来仅仅局限于哲学的狭小空间,注重哲学话语与其他社会话语之间的互动,注重哲学话语与社会建构之间的互动,使得道学话语研究深入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等相关研究领域,这一突破也使道学回归到其原有的“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恢宏格局,使道学研究不再被人为地肢解,从而回归道学的原初样态。但是这一改变也带来了话语分析的泛化和哲学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因而,在道学话语分析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文本与语境的关系、如何注重哲学话语的提炼、注重哲学话语的分析、注重话语的哲学特征也成为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三、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方法的操作途径:以道学话语系统(共同体)为例
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方法是对传统子学范式、经学范式、西学范式(尤其是范畴研究范式)等研究范式的承传、创新与超越,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中国哲学内部的关键话语与问题,它立足中国,与西方对话,凸现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如工夫话语与境界话语都是西方话语所无视的问题)。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旨在对中国哲学话语(文本、命题、实践工夫与境界)的语境、语义、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与西方话语分析方法有意疏离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与话语分析方法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哲学与其他领域。相当于西方话语分析,中国哲学话语分析方法更注重话语的过程性、时间性、建构性、实践性、你与我的对话、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联以及工夫话语所达成的境界。可见,话语分析虽然来自西方,但是中国哲学话语分析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工夫话语、境界话语、道德与政治的关联与对话等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这些新的话语理论形态,是对西方话语分析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话语分析方法是道学话语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方法论,该方法注重道学核心话语的分析,注重分析话语事件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把道学话语放进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脉络中展开研究。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操作路径如下。
首先,通过文本细读,确定所要分析的道学研究的核心话语。通过文本细读,深入文本,抓住文本的核心话语和时代核心话语展开分析,揭示被历史遮蔽的问题意识、时代主题及其解决之道,再现或还原思想史上遗失的重要环节。话语分析方法尽量用材料说话,暂时搁置主观价值判断,客观真实地揭示出文本特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旨趣。
其次,在数据库中进一步证实话语的核心地位。通过现有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韩国文集丛刊、日本儒林丛书等数据库,对道学核心话语进行检索,如果该核心话语在该文本和同时代及以后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几乎每一思想家都在反复讨论该话语,该话语的核心性就可以成立,该话语便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道学的关键话题。
再次,对该话语展开分析。深入文本和时代语境,对该话语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出该话语的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历史轨迹,阐释该话语的不同层次的含义,比较该话语在不同思想语境中、在不同思想家的视野中的不同含义并详细地分析其中的原因。话语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在话语分析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分析话语的社会建构、话语实践、道德与政治的关联性、工夫话语与境界话语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了解某一话语究竟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社会并取得何种效果,话语的社会化适应如何完成。
最后,在大量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建构道学的话语体系,分析其理论类型。其中,道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体认天理、理气先后、无极而太极、理即事,事即理、性即理、理气动静、心即理、理一分殊等),工夫话语(格物致知、主敬穷理、诚意正心、读书、静坐、体验未发之中、克己复礼、博文约礼、定性、慎独、拔本塞源、心统性情、事上磨炼、尊德性与道问学、操存省察、已发未发、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等),社会政治话语(正君心、出处、国是、教化等),境界话语(见天地之心、识仁、鸢飞鱼跃、孔颜之乐、曾点之志、自得、致良知、民胞物与、全体大用等)。在大量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构出道学话语系统,并分析其理论类型。[29]
道学话语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一个由道学家的思想与话语组成的话语共同体。陈来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较早关注道学话语系统的哲学家,他指出,所谓宋代道学话语的研究,是希望借鉴话语研究的方法,使宋代道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并使得对宋代道学前期发展的零散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获得方向和整合,从而使目前宋代理学的研究在单一的研究范式的状况下摆脱出来,走向新的、更为活跃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话语研究方法与西方话语理论关注文本与权力结构、符号与社会制度的联结不同,主要从学术陈述本身来看话语构型。从这方面来看,意义表达为陈述,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命题是陈述的形式化凝结;话语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来自命题、陈述的共同风格和共同主题,来自问题意识上的共识,也来自对关键概念使用的共同偏好,从而形成了话语体系。任何话语都是经过散杂、剔除、积累、集中的过程,才逐渐形成各个领域的话语系统。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传承,在中国又是和学派传承的意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道学无疑是一种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的过程,很值得加以细致研究,并总结、提炼出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30界定一个话语系统或话语共同体[31]的思想特质如下:(1)成员持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并且能辨识出他们之所以称为一个群体的一套超话语特征(意识形态);(2)社会化适应主要通过那些被认同的话语形式实现的(社会化适应);(3)一套被认同的话语形式是成员资格和身份旗帜或标识(话语形式);(4)界面关系由成员之间的话语或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话语规定(界面体系)(face systems)。[32]
在道学话语共同体中,道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特征)主要体现为七大法则。第一法则:天理(心)是最高的本体和原则,理想的社会是天理流行的社会。第二法则:个人目标是学为圣人,社会目标是回归三代。第三法则:尊崇道统,文化历史发展有它的连续性和周期性。第四法则:个体修养是获得个人幸福和社会认可的关键(为己之学、道德优先);个体是一个禀赋天理的实体,人性本善,但被欲望遮蔽,天理与人欲相互消长。第五法则:书院为道学社会化的主要推广模式。第六法则:内圣与外王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七法则:工夫话语及其实践是道学建构的中心。
道学话语的社会化适应包括:书院教育、讲会、社会教化和科举推动,其中书院教化是最基本的社会化适应模式。家族中的社会文化适应模式:父亲代表道德的权威。一个社会式话语系统所特有的教育和社会文化适应的理论是建立在其成员的善恶本性这一更为普遍的观念基础之上的。道学话语系统中的话语形式主要有:语录、集注、墓志铭、序跋、书信、行状、奏章、故事、说、诗文。理学话语的主要特征:公众性(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尊崇权威、先圣先王)、理性的、等级主义的(师生、圣凡、君臣、父子、上下)、群体主义的(或说道德主义的)、归纳的而非演绎的……道学话语系统中的界面体系区分为内部界面体系和外部界面体系,主要涉及道学内部的自我认同、道学群体内外的关系等。内部界面体系包括:公众话语(国家话语)、书院派话语(道学、心学话语等,具体分为湖湘学、婺学、永嘉学派、濂洛关闽、心学话语)。外部界面体系包括:非理学话语、异端(佛道)话语、其他话语等。
道学是关涉内圣外王的思想整体,是宋元明清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意识形态、界面系统和社会化适应模式。在应对佛老学说的挑战中,顺应宋代时代语境,道学应运而生。道学的本体话语、工夫话语、境界话语、社会政治话语等核心话语构成了其丰富的话语系统,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学话语秉承尧舜禹文武王周公孔孟的道统文化精神,坚持王道政治理想,倡导为己之学,关注“身心的修炼”(“哲学的修炼”),主张塑造道学新人格,书院教化是其社会化适应的主要模式。道学的工夫话语本身就是身心的修炼和哲学的修炼,是知行合一的工夫实践。其社会政治话语则建构了宋明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引领时代方向。在思想家的语录中,我们也能深深感受到道学家们直接的、当下的、平等的对话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力。总而言之,从话语建构模式上分析,道学上升为国家最高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话语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话语分析方法抛弃了以往以范畴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注重语篇和语境分析,关注话语实践,通过对道学的核心话语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道学的研究空间和理论内涵,一大批以前较少关注的道学话语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野。我认为,话语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将带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话语分析方法有它的普适性和独特性,它可以容纳西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和解释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理路,把概念、范畴视为话语片段、注重话语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注意到话语的差异性和断裂性,与先前的研究范式之间保持着连续性并不断推陈出新。话语分析方法能够回到中国哲学的原生态,回归内圣外王的整体性与统一性。话语分析方法注重本体、工夫、境界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其中,工夫话语是连接其他话语的关键,这一研究将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随着话语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一大批新的人物、新的文本、新的命题、新的话语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为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话语分析方法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它能充分表现中国人的生命情态、生命体验、生命境界和工夫实践,建立一种新的关联性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方法论的普及和推广,中国哲学研究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理论格局。
(原载《学术月刊》第48卷,2016年第9期,又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两岸协创中心、哲学系)“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
⊙陈逢源
一、前言
北宋诸儒昂然奋起,证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极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学发展历程中精彩的一页。濂、洛、关、闽相继而起,成就斐然,然而汇聚成果,有赖朱熹集其大成,完成重构经典工作[1],自此由理学入于经学,由讲论而及于经典诠释,成为儒学后续发展的重要事业,朱学传布与四书讲论,乃是一体之工作。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刘爚奏请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国学[2],理宗淳祐元年(1241)诏入学宫从祀,云:“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3]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颁《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定本。[4]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场试四书义,四书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宋代沦亡,元代继起,元朝既没,明朝接续,朝代不同,但都推崇四书,四书成为宋元以降学术核心。后人往往以政治威势来解释朱熹地位的提升,认为朱熹学术乃出于官方表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庆元党禁、局势汹汹之际,无法想象日后学脉得以延伸,学术得以拓展的情形,钱穆先生“虽有科举功令,然不得专以科举功令为说”[6],乃是相当深入中肯的说法。朱熹的坚持与门人后学的传播,印证义理,蓄积力量,由民间而及于官方,才是建立四书学术地位的关键因素。[7]南宋推崇朱熹学术,来自于既压复起,还以公道,恢复朱熹名誉;元代表彰《四书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取用乃是怀柔兼纳的手段而已,用意在于笼络士子。[8]同尊朱学,程度与用意不同,真正确立朱熹学术地位,主要来自于明朝态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旧,深有恢复传统的意义,考试以朱学为宗,已具气氛,然而贯彻帝王意志,以皇权威势整合歧异,建立朱熹为尊的经说体系,主要来自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命胡广等人纂修《四书大全》[9]。自此,朱熹成为学术宗主,四书成为后代最重要经典,《四书大全》成为明代士人成学、入仕最重要的经说依据。[10]《四书大全》的地位无可比拟,检视明儒言论,邹元标《愿学集》云:“惧学者溺于异指,令童习家学,见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图无疆之治。”[11]高攀龙《高子遗书》云:“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12]指出皇权政教一体之事实。清人陆陇其甚至直指:“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时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13]一学术,同风俗,明显可见政治操作的影响,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四书大全》,明代“官学化”的结果便是确立四书成为最重要经典。就经学发展而言,唐代《五经正义》整合义疏,完成经学统一,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之为“经学统一时代”[14];至于明代以《四书大全》统合元儒经说,皮氏以“积衰时代”[15]来称呼明朝经学,认为其为败坏学风的源头,立场明显矛盾。事实上,《四书大全》整合宋元四书讲论内容,一如《五经正义》统合汉魏以降的经疏成果。唐承汉魏,明继宋元,落实经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经典文本,具有同样的学术发展意义,然却深受误解!为求厘清,笔者针对《四书大全》“引用先儒姓氏”,核以《宋元学案》,撰成《〈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16],分析庞大征引来源,探究朱熹门人结集之后学脉、宗派而及于宗族乡里情怀不同阶段的传衍线索,得出结论:黄榦传学何基,北山一系称为朱学“嫡子”,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具有由宋入元,巩固学脉正传的地位,也具有确立朱学内涵的意义。《四书大全》征引共计106家,其中名列《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其中征引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四书大全》建立诠释体系的核心基础和得以溯及朱熹的关键,对于掌握义理方向深有启示。
二、北山四先生之四书学
朱熹之后,黄榦为学门领袖。[17]朱学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最为重要,他们代表了朱学之后传播开展的第一个阶段。统计朱熹门人籍贯分布,以第一传门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传门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传门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传门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传门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18]可见朱学三传之后,浙江人数逐渐增多,五传之后,更具有绝对优势。朱学由福建往传浙江,影响日趋深远,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按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19]黄百家(1643~1709)按语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峯亦高弟也。双峯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20]
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成为宋元朱学传播的中心,从脉络渊源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华人,从父命师事黄榦,黄榦勉以“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于病革之际对弟子的期许[21]。何基撰有《中庸发挥》《大学发挥》《论语发挥》,惜皆亡佚。核其语录,云:
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敬五事则明明德也,厚八政则新民也,建皇极则止至善也;至学皇极,有休征而无咎征,有仁寿而无鄙殀,则中和位育之应,皇极之极功也。
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中《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22]
前者发挥四书义理,后者深化四书义涵,不论是扩之于外或是究之于内,皆是以四书作为学术核心,《四书章句集注》与《朱子语类》相参的路径,更是指引后世解读朱熹四书学非常重要的方向[23],无怪乎黄宗羲按语云:
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晚年之论曰:“《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犹不满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应聘讲,第恐无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则,若人者,皆不
熟读四书之故也。”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24]
何基守之既严,甚至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树立熟读四书的学门宗风,正是传自黄榦学术的证明。
何基学术传于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王柏关注四书态度不变,同样强调必须深究其内而不必旁伸于外,语录云:“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盖深求之于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25]即可为证。王柏崇信四书的立场并无改易,不过细节上显然已有不同的思考,“虽曰”一句已透露端倪。王柏重视四书经文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甚于朱熹,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中庸》当依《汉书·艺文志》所载《中庸说》二篇,以“诚明”以下别为一篇[26,相歧之处,皆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建构义理诠释的重点。然而王柏尝试从结构化解改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王柏有关四书类著作,有《订古中庸》《论语衍义》《论语通旨》《鲁经章句》《孟子通旨》《标注四书》等,可惜大都亡佚。重构四书文本,其实是延续朱熹思考的结果,只是背离朱熹说法,尊背注而求经,奉与违戾之间,立场不免令人疑惑。[27]
金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柳贯《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云:
文公之于论《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之,其问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备也。而事物名数,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为之修补附益,成一家言,题其编曰《论语孟子考证》。[28]
补充名物,以备考证,用意在于补充而非阐释。《宋元学案》黄百家按语云:
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历时既久,思之甚深,诸多说法前后不同,甚至留有诸多待解之处,临终前为《大学》“诚意”章费心竭虑,更是人所熟知之事[30]。后人延续思考方向,尝试解决经典文本与注解诠释问题,乃是学术发展的常态。黄百家申明后人应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迹,无疑是通达而且正确的看法。金氏既守朱学之教,又发四书之义,有关四书之著作有《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其中《大学章句疏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皆收于《四库全书》之中。金履祥传之许谦,强调“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矣”[31],皆是朱学核心要义,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许谦于四书亦颇有心得,黄溍云: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敷绎义理,惟务平实。每戒学者曰:“士之为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至于进修利钝,则视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舍其书,何以得其心乎?圣贤之心,尽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立言,辞约意广,读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贸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觉其意初不与己异,愈久而所得愈深,与己意合者亦大异于初矣。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3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约意广,深嚼有味,许谦推崇至极,由朱子而得四书义理,由四书而得见圣人,饶富义理进程,只是许谦发挥义理,并不墨守朱注。《四库全书总目》云:“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33]重视四书,强调朱子,也留意缺失,补正朱注。[34]许谦有关四书著作有《中庸丛说》《大学丛说》《读四书丛说》。《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说》只是四卷残本,阮元从元板影录《论语丛说》三卷,又从吴中藏书家得元版《中庸丛说》足本二卷。[35]北山学脉由宋而及元,脉络清楚于此可见: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黄榦接续朱熹,设教讲学,推究义理,昂然挺立,成为宋元之际最重要的朱学重镇,一方面传播朱学,延伸学脉;另一方面阐释义理,开展议题,证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价值。诚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汉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于同也。[36]
以动态方式看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同之与异,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无古今,学无先后,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仆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37]。既不执拘定见,又深化朱学成果,四书遂有多元丰富之诠释内容。朱学由宋入元,由注进入疏解的阶段,学人在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辩证,不论是横向发展还是纵向深化,贡献良多,无怪乎明代章一阳以“正学渊源”为名,纂辑四先生著作《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38],视之为由宋及元四书学发展一个重要环节;清代戴锜亦以洙泗、濂洛、关闽、北山为一脉相承之体系,其云:
水行地中,千条万派,莫不从昆仑发源而来,犹夫学者穷经立说,传道解惑,有不自洙泗来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关闽,一脉相承,道统绵绵弗绝,何其盛哉!嗣后有造邪说以乱之,招歧途以引之,而终不能蛊惑人心,必以紫阳为传道之准,斯时知有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相与扶植而辅翼之,以为功之至巨者矣。而不知无何、王砥柱于干道、咸淳之间,必不能传于金、许,无金、许振兴于绍定、大德之时,又何能绵远于今兹也哉![39]
承袭濂、洛、关、闽,儒学得传,北山一脉学人地位于此可见。
三、《四书大全》征引之北山学脉
《四书大全》征引当中,名列《宋元学案》之《北山四先生学案》共计6人,分别为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征引情形如下:
征引量共计154条。北山一系学人的著作如今多数已经不传,《四书大全》征引其说,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尤其是在朱子学发展当中,北山一脉具有衔接朱门与后学的作用,对此后人深有共识。吴师道为许谦《读四书丛说》撰序言之甚明,其云:
《读四书丛说》者,金华白云先生许君益之为其徒讲说,而其徒记之之编也。君师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师鲁斋王先生柏,从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门,北山则学于勉斋黄公,而得朱子之传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中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之后,不泯灭而就微,则泮涣而离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40]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41],对于后世建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方式,具有关键地位。明代《四书大全》援取疏解内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际朱学传布情形,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体系,未见何基言论,恐与何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42]的态度有关。至于王柏、金履祥、许谦当中,许谦征引最多,则是因为许谦为入元之后发扬朱学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学列传》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43]
许谦于元代,讲学四十载,授徒著录千余人,发扬朱学不遗余力,撰作既丰,成果斐然,成为《四书大全》重要征引对象,乃是理所当然。此外,北山一系学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欧阳玄、何梦桂(《四书通》《四书大全》皆作何梦贵)、方逢辰三人。欧阳玄,字原功,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博,列于“仁山门人”,有《圭斋文集》传世。方逢辰,字君锡,学者称蛟峰先生,学术“以格物为穷理之本,以笃行为修己之实,终身顾未尝有师承”[44,然而父亲方镕为“朱学续传”,家学渊源,同是朱学一脉:
彼亦有以颖悟为道,以卤莽灭裂为学者,其说谓:“不由阶级,不假修为。”以致知格物为支离,以躐等陵节为易简,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匪徒诬人,亦以自诬,天下未有一超径诣忽焉而圣贤者。
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学之博以积之,反之约以一之。[45]
重申格致之教,阐明穷理之功。由四书而六经,学而有序,归之于理,提供了一条有进程、有境界的儒学道路,体系俨然。至于易简之教,直接圣人,不仅是自诬,而且也诬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陆,立场至为明显。然而于学术推展,北山一脉学人彰显朱学,也有与陆学争是非的意义。何梦桂,字岩叟,学者称潜斋先生,与方逢辰为讲友,宋亡不仕,于艰困之中昂扬挺立,于家国沦亡之际慨然承传,在山林乡野之间讲授不辍,具有以身体道的实践意义。[46]事实上,朱熹对于吕祖谦死后的浙东学风深有疑虑,永康功利之学、永嘉事功之学继之而起,一重实利,一重实事,然而求之于外的结果,违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为利所诱。为求厘清,朱熹特别表彰金华先儒范浚,并将《心箴》载于《孟子集注》当中,以乡贤前辈的名望对治后学驰功逐利的缺失,期许从功利之中回归于人心救赎。47可见往浙东开展乃是朱熹夙愿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学人由黄榦而继承朱学,另一方面浙东本身也有其学术传统,吕祖谦于丽泽书院和明招堂讲学,门人众多[48]。金华原就是众多学派思潮交会之地,陆学、永康学、永嘉学相互交流,深有调和色彩。《朱子语录》卷122载有朱熹之分析,其云: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而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吕祖谦兼纳博采,重史轻经,成为浙东学术的特色。然而朱熹认为根源不明,不免于关键处偏失,而重权谋,求功利的结果,则不免让人违弃仁义,最终让人误以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论语》救治偏蔽,强调在日用之际,在心念之间,高举仁义价值,坚持儒学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后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也是采取相同立场。朱熹对于浙东学风深有忧虑,于此可见。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学与陆学的道学砥柱”为标题,说明朱熹于南宋尚虚、尚实学风之间,展开全方位文化论战,在南宋纷然并起的学术社群当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颇能说明朱熹学术的方向。[49]而门人黄榦往浙东传学,不仅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北山一系学人习之有验的结果,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熹学术最终得以胜出。只是学术面相更为复杂,朱学既从北山一系学人而深入于浙学,却也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诠释方式,学术既延伸又相互影响,也就无怪乎《宋元学案》黄百家一方面有“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有“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的观察,甚至于最后又云:“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50]。黄百家出于浙学,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学于浙学发展中入于史,通于文[51],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四书义理愈加丰富,却也渐生歧见,其中矛盾,正来自于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的结果,尤其后人缺乏朱熹融铸义理、思之甚深的历程[52],各自揣想之下,于经文兴发议论,时见新意,也时有误解,甚至以纠弹朱熹说法作为个人学术成就,不仅混淆朱熹四书义理体系,也造成后人了解的困扰。此一情形,从后人论述当中可以得见。邓文原《四书通序》云:“近世为图为书者益众,大抵于先儒论著及朱子取舍之说有所未通,而遽为臆说,以衒于世。余尝以谓,昔之学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学者常患其不胜古人,求胜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53]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云:“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54]议论纷出,各立门户,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学人。“争奇取异”的结果,孰为正解,顿成经典诠释的重要问题。以朱熹为宗成为后人最终的方向,回归于朱学则成为建构诠释主轴最重要的诉求,此一主张于新安一系宗主乡贤前辈的气氛中开展[55],而于明代完成。明代四书官学化过程中,确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种整合学术的手段,也是尝试解决朱学传衍问题的途径。[56]发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书经说内容,于后人剔除歧出、化异求同的调整当中,纳入官学系统,成为《四书大全》申明朱熹四书体系,阐释朱熹诠释经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学术传衍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发展意义。
四、诠释转折与开展
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金履祥考证四书的内容,《四书大全》收录不多,有关名物训诂的资料,《四书大全》以张存中《四书通证》为主,原因所在,可以由其言“学者于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于《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着所出”[57]一窥端倪。考证后出转精,张存中以补其所出的角度,内容更为丰富,自然成为《四书大全》取用材料。至于王柏有关《大学》《中庸》文本结构的调整,也并未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材料当中,显然关注所在,已有不同。其次,以征引的数目分析,《四书大全》征引许谦材料,《大学》29条,《中庸》34条,《论语》22条,《孟子》33条,数目相当平均,然而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分量之悬殊,即可发觉其中有异。许谦有关《大学》《中庸》诠释成果,征引比例明显较高,如果与其他人加总计算,《大学》42条、《中庸》43条、《论语》30条、《孟子》39条,《大学》《中庸》征引比例明显偏多,至于《论语》则明显偏少。检核《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大学》《中庸》各有一卷,《论语》四卷、《孟子》四卷,共计十卷,《论语》《孟子》并无空缺,经过后人筛选拣择,《四书大全》似乎更加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诠释成果,而对于《论语》《孟子》部分关注不深。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四书进程、体系与境界的讨论,对于四书义理的兴趣,高于日用之间、事理之际的体悟。朱熹对于浙东学术曾有“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28]的针砭语,似乎也反映于《四书大全》征引当中。事实上,检视《四书大全》列举方式,小注以朱熹《语类》、《或问》内容为主,后文辅以弟子门人意见,最末则以“云峰胡氏”“新安陈氏”“东阳许氏”等元儒诠释作结。分析征引结构,前者可见朱熹讲论之义理方向,后者可见训诂与体例的补充,形成朱熹、门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经说体系,元儒经说部分,多数依循饶鲁、新安、北山三系为序,而许谦说法往往列于征引之末,借以阐明章旨的价值与意义。可见北山一系作为朱学由宋而及元的最初发展阶段,也成为后人讨论的基础。后人赓续推究,进行更全面的四书义理思索,其中排序并非偶然。北山一系学人深化与开展之处,列举如下:
(一)推究工夫进程
训解经文为《四书大全》征引内容的大宗,收录北山一系学者意见也以此类说解最多。分析语意,也辩证义理,北山学人一脉相承,经典诠释有继承发展的现象。《大学章句》朱注“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引许谦、方逢辰云:
严密,是严厉缜密。武毅,是刚武强毅。以恂栗释瑟僩,而朱子谓恂栗者,严敬存乎中,金仁山谓所守者严密,所养者刚毅,严密是不麤疏,
武毅是不颓惰,以此展转体认,则瑟僩之义可见。
瑟是工夫细密,僩是工夫强毅,恂栗是兢兢业业。惟其兢业戒惧,所以工夫精密而强毅[59]。
金履祥分出所守所养有严密与刚毅的不同,许谦、方逢辰的诠释乃是承前发展。《孟子集注·告子上》“乡为身死而不受”章引许谦云:
三乡为身,北山先生作一读,言乡为辱身失义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为身外之物,施惠于人,而受失义之禄乎,可谓无良心矣。[60]
申明经旨,乃是引用何基说法,诠释层层累聚,于此可见。北山一系学人彰显经典旨趣,揭示其中要旨,最终往往归于修养工夫的思考。《大学章句》“《诗》云:‘瞻彼淇澳’”章引许谦云:
此节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谓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绪,谓先切琢而后可以磋磨,循序而进,工夫不辍。切磋以喻学,是就知上说止至善,讲习讨论,穷究事物之理,自浅以至深,自表以至里,直究至其极处。琢磨是就行上说止至善,谓修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直行至极处。瑟兮僩兮谓恂栗,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谓威仪,是德见于外者著。[61]
切磋琢磨,止于至善,许谦由知行两端,说明工夫所在,诚敬存乎中,尚不足有美盛德之形容,唯有达于至善,内恂栗而外威仪,融通内外,德容充溢表里。儒学有工夫、有进程,丰足饱满,由经典以入圣人之境,更有自信。《中庸章句》“诚者,天之道也”章引许谦云:
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择者,谓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谓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择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62]
以格物穷理说解经典意涵,择善而固执正是内外交养的结果。《大学章句》“所谓诚其意者”章引许谦云:
诚意只是着实为善,着实去恶。自欺是诚意之反,毋自欺是诚意工夫。二如,是诚意之实。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诚意之效,慎独,是诚意地头。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诚不诚,皆自为之。自欺者,适害己;不自慊者,徒为人。恶恶臭,好好色,人人皆实有此心,非伪也。二如字,晓学者当实
为善去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为也。[63]
以实释诚,途径直接明朗,为善去恶一出于诚,工夫纯由自己,无丝毫勉强,许谦确实掌握朱学的精神。《孟子·告子上》“操则存,舍则亡”章引许谦云:
浩然章论养气,而以心为主;此章论养心,而以气为验。曰志者气之帅,故谓以心为主。曰平旦好恶与人相近,故谓以气为验。集义固为养气之方,所以知夫义而集之者乃心也,养心固戒其梏亡。验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则气也,彼欲养而无暴,以充吾仁义之气,此欲因气之息,以养吾仁义之心。两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尝不同,而气则有在身在天之异,然未始不相为用也。[64]
这番话对心与气的关系言之甚详,养心验气,养气由心,唯有心气交养,才能仁义充盈,指出儒学极为重要的修养方法,以及朱学重要学理内容,诠释深切到位。《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章引王柏云:
“善推其所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65]
孟子开展仁义,正是善推其所为,学问在此,修养亦在此,儒学精神于此显豁,可见经典阅读的深入与精彩。当然其中也有理解偏失之处,《中庸章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章引许谦云:
程子谓不偏之谓中,固兼举动静。朱子不偏不倚,则专指未发者。[66程子兼有动静,朱熹仅言及未发之中,许氏辨别程、朱有不同的诠释重点,但对于朱熹融静于敬,涵养更密的思考,体会不深。《四书大全》载录朱熹弟子陈淳之言,云:“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可谓确而尽矣。”67朱熹取程子之说,推而及于内外动静,内涵更为周延细腻,许氏未能详究朱熹中和之悟的进程[68,观察并不深入。《大学章句》“物格而后知至”章引许谦云: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谓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揍合将来,遂全其心而足应天下事矣。[69]
“而后”既是顺序之词,也是一种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关乎工夫进程,兹事体大。《四书大全》引朱熹之说云:
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着“而”字,则是先为此而后能为彼也。盖即物而极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无不至。吾知无不至矣,而后见善明、察恶尽,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诚。意无不诚矣,而后念虑隐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70]
格物乃是修养的关键,即物穷理,知明而意诚。就工夫而言,朱熹有深刻的思考,所谓“先为此而后能为彼”,正是强调其中顺序不可紊乱,以及学术进程的安排,此为朱学工夫论的核心。然而浙东学术贵通达,许谦对此却有一种转折性的诠释,强调“致知力行”并进,于是一物之格,诚意、正心、修身乃是同时进行,最终期许逐渐理会,全其心以应天下之事,于是工夫所在,一次到位。说法是否符合朱熹原旨,有待深入讨论,但对于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因此“终身无可行之日”的逻辑问题,遂有可以解决的方向。
(二)阐明境界所在
朱熹以一生建构四书义理,如何确立有效理解,乃是后人研究的首要之务。《中庸章句序》引许谦云:
《章句》《辑略》《或问》三书既备,然后《中庸》之书,如支体之分,骨节之解,而脉络却相贯穿通透。[71]
此一方法与黄榦强调直究原典,以《章句》为研读根本的方式不同。72黄榦标举的方法,目的在于避免淆乱,然而浙东学术重视文献,更加留意考据的趣味,取径开阔,以《章句》为本,佐以《辑略》《或问》的研读方式,有助于了解朱熹思考进程,转折之间,《中庸》义理得以显豁。有关研读方法的指引,也见于《读中庸法》引许谦云:
《中庸》《大学》二书,规模不同。《大学》纲目相维,经传明整,犹可寻求。《中庸》赞道之极,有就天言者,有就圣人言者,有就学者言者,广大精微,开阖变化,高下兼包,巨细毕举,故尤不易穷究。[73]
《大学》言纲领,《中庸》明境界,研读方式,朱熹原就有安排,其云: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74]
《中庸》标举天道、圣人,期许学者有以继之,许氏所言确实符合其中旨趣。至于《章句》《或问》相参方式,提供深入朱熹义理思考细节,《中庸或问》引方逢辰可以为例,其云:
《或问》中旧说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句,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盖谓有主张是者,而实未尝有所为耳。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直谓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二说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谓鸢鱼之飞跃,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处,勿正心,谓无勉强期必,非有心着意也。活泼泼地,是指天理呈露处,此朱子旧说之意,就鸢鱼上言。今说却就看鸢鱼之人上言,谓就费视隐,必自存其心,则道理跃如矣。朱子谓只从这里收一收,这个便在,朱子两说皆精,但前说恐人无下手处,故改从后说之实。[75]
朱熹为免蹈空入虚,前后之间,趋之于实,朱学最终精神的趋向所在,于此可见。事实上,浙东学人强调文本结构,《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章引许谦云:
此章专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细微处不合道,而于远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势必当如此。故于费隐之后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谨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则言正己不求于外。此章则言自近及远,是言凡行道皆当如是也。引《诗》本是比喻说,然于道中言治家,则次序又如此。[76]
《中庸章句》“君子之道,费而隐”[77,循此而下,第十三章阐明以恕行之,第十四章说明正己不求于外,第十五言行道自近及远,层层而进,彼此衔接,各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申明由近而及远,日用之间,道无所不在。许氏善用文学分析手法,章旨可以据此而得。此外,比较两章之间手法,也可以了解经旨所在。《中庸章句》第三十章朱注“言天道也”引许谦云:
二十六章言圣人至诚,与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则圣人之盛大自见。此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道,自万物并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则圣人之大自见。前章则引文王之诗以结之,此章则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礼,无非形容圣人之德也。[78]
圣人与天地同道,许谦比对《中庸章句》第二十六章、三十章,同样是言天地之盛大,以见圣人之盛大,铺排方式相同,至于二十九章引《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79为结,三十章则以“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80]破题,前者为文王,后者为孔子,圣圣相承,彼此衔接。至于以孔子作结,《中庸章句大全》“仲尼祖述尧舜”章引方逢辰云: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书之末,以仲尼明之。[81]
可见文本具有内在的肌理脉络,经典意义结穴所在,揭之而出,遂能彰显结构用意。经典本身原就有圣圣相承的线索,既承继而发展,又遥接而发挥,圣道境界遂有其理据。朱熹分享经典阅读经验,言“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却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821。读经必须从章句文字的语意层面,深入于文本结构当中,推敲全篇旨趣所在。浙东学人延续朱熹思考方向,诠释更趋务实。《大学章句序》“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一句引许谦云:
规模节目,以三纲八条对言,则三纲为规模,八条为节目,谓八条即三纲中事也。独以八条言之,则平天下为规模,上七条为节目,平天下是大学之极功。然须是有上七条,节节做工夫,行至于极,然后可以平天下。[83]
以《大学》而言,三纲为规模,八目为节目,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84],两相搭配,乃是极为适切的诠释。但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延伸,离三纲而言八目,以平天下为规模,格、致、诚、正、修、齐、治为节目,不无可疑,毕竟缺乏明明德之根本,八目不免有外驰之弊。或许对于元儒而言,平治天下乃是儒者事业所在,也是儒学规模所在,儒学境界于经旨当中获得启发,外王事业也是儒学的究竟,因此寄以无限的期许。许衡留意经文结构,于是将规模与节目视为境界与进程,将三纲与八目视为两个独立文本,然而北山一系学人重视外王事业,于此可见。
五、结语
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义理推究深微,四书成为学术核心。在宋元学术纷出之际,北山学人证明朱学价值,饶富学术发展意义。《四书大全》征引的仅是部分内容,自然无法代表全貌,然而重视工夫,强调境界,北山一系学人融通经学与理学,厘清四书文本内涵,在经典诠释当中彰显朱熹学术价值。经由北山一系学人的努力与尝试,明儒四书经注诠释体系才能完成。只可惜北山一系学人为朱学嫡子,然而承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并不明显。《孟子·尽心下》由“孔子而来”章引胡炳文云:
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极功。学者不知所向,则非有志于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则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趋向之正,造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为明道矣!真知明道,则真知尧舜以至孔孟者矣!善乎勉斋黄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朱子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则《集注》所谓百世而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当自见其有不得辞者矣。[85]
胡炳文乃是新安一系的学者,黄榦推崇朱熹为百世而下心领神会之人,北山一系学人经由黄榦溯源于朱熹,以身份而言更为纯粹,对于朱熹道统应有进一步的说法,但是征引情形并不明显,相关论述几乎集中于新安一系学人。元代不同宗派,不同学术系统,彼此相互竞逐,《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或许出于明成祖排除明初开国浙东学人势力的一种手段。[86]然而学术积累,北山一系学人诠释心得,终不得掩,观察征引情形,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黄榦彰显朱学,以传道为己任,以影响层面而言,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学人世系绵长,代有名儒,金华既是宋元学术重镇,也是宋元朱学传播中心,称之朱学“嫡子”,确然可信。
其二,朱熹从北山一系而深入于浙学,却也不免濡染浙东以史证经、务求博通的倾向,学脉继承与学风交互濡染,其结果,朱学开枝散叶,枝脉扶疏,影响愈深,也难免渐生歧见。
其三,检视《四书大全》征引情形,北山一系经说以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四书大全》留意北山一系学人《大学》《中庸》的诠释成果,对于《论语》《孟子》关注不深。
其四,北山一系学人对于四书推究深微,《四书大全》征引特别留意儒学修养工夫,也关注儒学境界所在,贯串绵密,融通经学与理学的思考方式,奠定了义理开展之基础。
其五,黄榦表彰朱熹,四书、朱熹、道统三位一体,北山一系学人虽然为朱学嫡子,号为正传,然而《四书大全》最终取新安而抑北山,而延续黄榦道统论述成果的,却是新安一系学者。
北山一系学人乃是传承朱学的重要学脉,也是《四书大全》建构经疏体系的重要基础,只是几经转折,分析结构、推究含义,遂有不同的思考,后世儒学重要主张,隐然已见于《四书大全》征引北山学人的言论当中。工夫期许知行并进,境界强调内圣外王,对于明代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清初经世致用之学,饶有启发作用,更可见北山一系学人深层影响。只是无可讳言,《四书大全》征引内容既多且杂,梳理不易,分析脉络,尚多疏陋,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原载《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
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
⊙〔日〕川原秀城 申绪璐 译 吴震 校
朝鲜朝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派大军侵略朝鲜。这场战役(包含休战期)前后长达七年(1592~1598),此即倭乱(文禄、庆长之役)。另外,在仁祖期间,后金(清)军队两次(1627、1636~1637)入侵朝鲜,此即胡乱。倭乱、胡乱的战祸是未曾有过的,使得朝鲜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朝鲜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的朱子学权威开始下降,其对政治社会的思想影响力也已大不如前。
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因为社会变动而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上的回应方式。其一是肯定传统价值,重视历史传承,对于固执于“社会模型”的保守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进行重新组合与强化;另一种则是绝对地信赖理性,正视“社会现实”,实行革新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的变革。在笔者看来,在朝鲜朝后期,前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统治思想的绝对化,后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的相对化。
在朝鲜思想史上,最先有组织地推进朱子学的绝对化(教条化),是刚进入朝鲜朝后期时出现的宋时烈(1607~1689)。宋时烈重视朱子学理念的原理和原则,并将其绝对化,即:(1)通过理论整理以证明朱子学整体的正确性(无谬性);(2)作为社会全体绝对的指针进行广泛的普及;(3)回归根本的理念并追求严格的应用,以此克服朝鲜社会的危机。宋时烈自定的使命即“明天理正人心,辟异端扶正学”(权尚夏《尤庵先生墓表》)。宋时烈政治思想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可由朝鲜朝后期的政界与学界中老论与宋时烈学派的持续兴盛得到证明。
另一方面,革新主义的朱子学者面对倭乱、胡乱之后的社会思想危机,正视两班社会的矛盾,拒斥教条(独断学说)而将朱子学相对化,试图通过推进思想的自由和灵活的社会应对以克服深刻的危机。这是因为朱子学业已丧失活力并严重衰退,很少有人还会原封不动地信奉其教义,也很难再对体制性教学的作用寄予期待,而更高层次的“义理”本身则与此相反,乃是天下共有之物,拥有无穷、无限的可能性。
尹䥴(1617~1680)与朴世堂(1629~1703)等人,与宋时烈一样正确地认识到朱子言论中的同异矛盾,以朱子定论(主要是《四书集注》中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再考察,或者通过对朱子定论与其他朱子言论进行对比,以此提出与朱子定论不同的观点并主张自身正当性。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将朱子学相对化、灵活化。另外,郑齐斗(1649~1736)则认真地研究阳明学,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四书解释等方面。虽然不能确定他是否是阳明学学者,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在朱子独尊的朝鲜社会中,朱子学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化。
初期的革新主义者超越以往的范围,构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但他们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论,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看,都是不充分的。具备思想实质的真正的社会改革论,还要等到朝鲜朝后期18世纪实学(朝鲜实学)的登场。实学之名原是指向实用之学问,然而朝鲜朝的实学家一方面重视保持朱子学的框架和严格区分传统与异端;另一方面又主张即使是异端之言,若有可观之处,亦必须学习,并且鼓励超越朱子学的范围(甚至不避攻朱),对于包含实用之术的广泛领域进行研究。[1]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分析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以期阐明朱子学相对化的内在实质。[2]具体而言,分析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与洪大容(1731~1783)的朱子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互相纠缠的思想性格,即宗朱与攻朱的奇妙混合(既保持强烈的思想正统意识,在本质上对异端思想采取非宽容之态度的同时,又积极地研究异端思想,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朱子学体系),以期论证这样一个问题:西学在作为朱子学相对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朝鲜实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李瀷的学术
李瀷,字子新,自号星湖,祖籍为京畿道骊州,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朱子学者、西学者之一。[3]
(一)强烈的道统意识与异端的西学研究并存
李瀷的一生,经受了17世纪末激烈党争的冲击,他是经常生活在政治剧变之阴影中的两班知识人。其家族为科举合格者辈出的南人名门,曾祖父李尚毅为议政府左赞成,祖父李志安任司宪府持平。其父李夏镇亦为司宪府大司宪,肃宗六年(1680)遭遇了南人大黜陟(又称庚申大黜陟)事件,随之失职而被流放到平安道云山。
肃宗七年(1681),李瀷出生于其父的流放地。第二年,其父李夏镇去世,李瀷随母亲移居先祖坟墓所在的京畿道广州的瞻星里。李瀷资质聪颖,优于常人,但是生而病弱,无法外出就学,其学问主要得益于稍稍年长的仲兄李潜。
但是仲兄李潜于肃宗三十二年(1706),以老论金春泽等人企图危害王世子为由而上诉,要求撤换老论的右议政李颐明,引发了肃宗的愤怒,拷问之后而被杖杀。仲兄因党争而惨死,李瀷为此而受到极大的冲击,失去了立身出世以及关心世事的意愿,从而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学习,此后作为在野的学者而专心于读书和著述。英祖三年(1727),虽被推举为缮工监假监役,他力辞而无意仕进。英祖三十九年(1763)去世,享年83岁。
李瀷的学问大致由三方面组成:(1)在吸收朝鲜朱子学(性理学)一派的李滉(1501~1570)思想的同时,(2)对于欧洲传来的新知识(西学)亦有正面的评价,并以此展开了新考察,另外,(3)受到柳馨远等人经世论的影响,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主张。[4]
李瀷学问的根本在于性理学,[5]其学统属于退溪李滉→寒冈郑逑(1543~1620)→眉叟许穆(1595~1682)传承的畿湖南人一系。但是,李瀷不止于将自身的师承系于李退溪,而是从个人内心出发,十分仰慕退溪的学德。因此,李瀷模仿《近思录》编集了收录退溪言行的《李子粹语》,以及为退溪的四端七情论辩护的《四七新编》,从退溪的遗集中分类抄出与礼相关的书札而编纂了《李先生礼说类编》等。另外,李瀷希望通过研究经书和性理学书来把握真理,以供社会之实用。这一点可由保存下来的有关《诗经》《尚书》《周易》三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以及《家礼》《近思录》《心经》《小学》等大量读书笔记得以证明。《诗经疾书》《书经疾书》等便是此类著述。
李瀷将继承与发展朱子学说作为其一生的志向,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如果反朱子学者的异端言论中有不得不看之处,亦应当学习。他积极地学习西学,果断地利用西学知识来解释儒家经文,并提出多种社会改革论。真正的学者必须为了振兴正学而批判异端,但是李瀷不受此拘束,而是在了解异端的同时,视西学研究为学者之当为而予以肯定,不得不说这是作为朱子学者不应有的态度。
在维持朱子学所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之同时,对于必须拒斥的异端却予以宽容,关于这一点或许应当做这样的解释最为稳妥:“这是一种承认其他思想也有部分价值的有限的多价值主义。”[6]
(二)星湖西学的概要
朝鲜朝景宗四年(1724)春,慎后聃拜访李瀷而了解到所谓“西洋之学”,于是,多次就西学问题,与星湖发生了论争,相关记录便是《遯窩西学辨》。该书大致由《纪闻编》《灵言蠡勺辨》《天主实义辨》和《职方外纪辨》所组成。《纪闻编》的撰写目的在于介绍星湖西学的概要。
基于慎后聃的《纪闻编》,可以看出李瀷西学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虽然李瀷自身最终否定基督教神学,但并不认为西教是耶稣会的阴谋(“张伪教而陷一世”),西学以外的西教也可成为分析考察的对象。例如,尽管慎后聃批评“天堂地狱之说”等西教理论的荒唐性,但是李瀷却介绍了西学的“实用处”(科学内容)强调其有用性,拥护“利西泰之学”。这与后文讨论的洪大容认为西教不值一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特征是,将脑主知觉说(“头有脑囊,为记含之主”)与三魂论(“草木有生魂,禽兽有觉魂,人有灵魂”)作为西学的核心命题。[7]甲辰(1724)春,针对慎后聃的西学“以何为宗”的问题,李瀷自己以“论学之大要”提出上述二说,可见上述说法是可以确定的。另外,戊申(1728)春,慎后聃曾对李翊卫提及,李瀷认同这样的命题。
所谓脑主知觉说,即“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李瀷《星湖僿学类选》的《西国医》以汤若望《主制群征》(1629年刊行)为依据,论述了“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这一观点,将西医的脑主知觉说与东医的心主知觉说予以折中,认为在人类的两大精神作用中,“感觉与知觉的作用在脑,思考与理性的作用在心”(“觉在脑而知在心”)。另外他主张一身流行的形气粗大,主思的心气(心脏之气)则极其细微,而它们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所谓“三魂论”,这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灵魂论,认为草木只有生魂(生长之心,anima vegetabilis),禽兽有生魂(生长之心)和觉魂(知觉之心,anima senseitiva),人有生魂(生长之心)、觉魂(知觉之心)和灵魂(理义之心,anima rationalis)。若将《星湖全集》卷四十一的《心说》、卷五十四的《跋荀子》以及《星湖僿说类选》的《荀子》合而观之,毫无疑问,李瀷所说的三魂论的论据与《灵言蠡酌》《天主实义》的灵魂论以及《荀子·王制篇》的“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有义”非常相似。
第三个特征是,李瀷认为“天文筹数法”“星历象数学”是“发前人所未发”或“有前古之所未发者”,极其称赞。[8]乙巳(1725)秋,李瀷解说了十二重天、温带凉带、地圆、日月行度、去极远近等,并记述了日月食预报的正确性。另外他还指出,郑玄的“地厚三万里”与西历的“地围九万里”是暗合的。
李瀷对于西欧数理科学的称赞在《纪闻篇》以外的很多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比如根据安鼎福《天学问答》的附录,李瀷指出西欧的“天文推步、制造器皿、算数等术,非中夏之所及也”。尤其称赞“今时宪历法,可谓百代无弊”,“西国历法,非尧时历之可比也”。[9]
(三)星湖的四端七情论
李瀷的心情论、四端七情论是退溪以来朝鲜朱子学内在发展的优秀成果[10],但同时必须承认其性理学的命题中也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李瀷的四端七情论,虽说是沿袭李滉以来的理气范式,但是吸收了奇大升(1527~1572)开始倡导而由李珥(1536~1584)集大成的心发的理气不离的基本原理,并借此重新解释李滉主理的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具体到心情论所讨论的心之机能与构造的问题,李滉以宋代张载“心统性情”为理论根基,从“性”“\情”观点出发论心,而李珥受元代胡炳文“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大学章句大全·经一章》小注)的启发,与性、情一样重“意”。对此,李瀷则在性、情、意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论点的变化以及论题的扩大。这与朝鲜朱子学的不断扩大进而发生变质的发展趋向是吻合的。
1.三魂论的影响
李瀷为了证明李滉理气互发的合理性[11],提出了严格区分知觉与思考的公私二情论,即将人心(七情)归属于“知觉之心”(私情),而将道心(四端)归属于“理义之心”(公情)。另外,为了论证源自公私的人心道心说的合理性,通过草木之心、禽兽之心与人类之心的对比,分析人所具备的心之构造。[12]
在《心说》一文中,李瀷认为虽然土石是无心的,然而“人者,较之于草木而均有生长之心。较之于禽兽而有知觉之心。其义理之心,则彼草木禽兽所未有也”。又说:“至于人,其有生长及知觉之心,固与禽兽同,而又有所谓理义之心者。”在星湖看来,植物、动物与人类之心具有如下的分层构造:
草木仅有生长之心
禽兽有生长之心与知觉之心
人有生长之心、知觉之心与理义(义理)之心在李瀷看来,知觉之心为人心,即人情,而理义之心为道心,即四端。
李瀷所说的草木、禽兽、人类的进化分层的心论,其构造非常独特。显而易见,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在内容或构造上都基本相同。另外如前所述,李瀷曾经通过《灵言蠡酌》与《天主实义》学习了欧洲哲学的心情论(三魂论)。由此可以断定,李瀷的公私心学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2.脑囊论(大气小气说)的影响
李瀷在其四端七情论中,论述了心情的发现路径与感应路径,其发现路径由道心(四端)的理发(理直发)与人心(七情)的气发(形气发)的互发二路所构成;相对于此,感应路径则是伴随发现路径而来,两者都属于理气共发的“理发气随”一路。
李瀷提到,首先,性“感物而动”,此时生发作为“性之欲”的情(《礼记·乐记》),四端、七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吾性感于外物而动,而不与吾形气相干者,属之理发。外物触吾形气而后吾性始感而动者,属之气发。”(《四七新编·第八》)“四端不因形气而直发,故属之理发。七情理因形气发,则属之气发。”(《四七新编·重跋》)在李瀷看来,理发意味着理的直接发动,与此相对,情的发动即气发是外物触及形气即身体,从而产生身体感觉(由外部刺激产生的身体感觉),再传达至心,最后理(或者思考、理性)发动(可参见出于李瀷之手的《四端七情图》,如右图)。李瀷所说的气发,由触及形气(身体)而生发,故以此命名,但是从发生的主体来看,则依然是理发而已。
在李瀷看来,心的发现路径有理发(理直发)与气发(形气发)两路,但是紧随发现路径而来的感应路径则只有理发气随(理应气随)一路。他说:“理发气随,四七同然。而若七情,则理发上面更有一层苗脉。所谓形气之私是也。”(《四七新编·重跋》)“心之感应,只有理发气随一路而已。四七何尝有异哉!”(《答李汝谦庚申》)关于星湖心学的“心发”构造,可以表示如下:
四端=道心(道德的情感)理发气随
七情=人心(由知觉而生的情感)生于形气之私→理发气随
须注意的是,在李瀷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的心发说当中,就发现而言,讲的是理气互发;就感应而言,讲的则是理气共发。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理论上的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李瀷指出,七情气发之气是指形气,与理发气随之气并不相同;所谓七情之气发,是指理发气随的知觉依形气而发。他说“气有大小。形气之气属之身,气随之气属之心。形大而心小也。”(《答慎耳老辛酉》)这是说,形气(一身混沦之气)与心气(神明之气)在大小差异及灵妙上的不同,而其作用也是根本不同的。
尽管李瀷的二情论可以说是以二情的绝对区别为其特征的,但是之所以说二情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最终的感应路径(思考)虽然一样,但是其发现路径(知觉与思考)却是不同的,故而知觉与思考的作用部位是有差异的。李瀷自身虽未明言,但是不得不说一种心理学的命题,即如下的心理二重构造乃是其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细微的神明之气相关的构造是“心↔思考↔理发气随”,与缺乏灵妙的粗糙形气相关的是“脑↔感觉↔气发”。
如前所述,李瀷通过分析《主制群征》所说的西洋医学知识,了解到气有
图1《四端七情图》大小粗细,而大小的不同导致各自机能的差异;断定感觉与思考是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上述两个命题,都与星湖的人心道心论非常吻合。星湖在构建其公私心学之际,很有可能是援用了这两个命题,以此作为其思想的前提。这是因为心发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之模型,即“知觉之心”的一身流行的形气为大,“理义之心”心气为小,同时感觉与思考是来自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这完全可以对应于西欧的医学理论。
3.中西会通与西学的理论优越
李瀷作为朱子学学者,他坚信儒学在整体上的正确性(“无谬性”),同时作为西学者,他所追求的是更高层次上统一中西两学,即17~18世纪西学研究者共同的理想“中西会通”。因此在他的论述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从东亚视角出发,来实现东西理论的无矛盾统一,并以经学理论为优的立场来加以整合或折中。在上述的四端七情论以其及论文《天行健》和《跋职方外纪》当中,我们便能看到这样的主题。
(1)《天行健》
《星湖僿说·天地门》中的论文《天行健》根据《易经·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说明西欧传来的天动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此天动认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三垣二十八宿天、宗动天等,都是围绕宇宙中心的不动的地球而公转的。
李瀷认为,《广雅》载“天之距地二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则说“五亿三千三百七十八里有奇”。两种说法,何者为是,尽管今天难以确定,但是两说都主张天是巨大的物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天既然是巨大的物体,因此不可能一日一循环(“一日一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周即对“天动”提出疑问,其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庄子·天运》)因为在理论上,即便是“地动”说,也能很好地说明天文现象。
但是,中国宋代朱子对于同样的问题,指出“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即天一日一转,地亦随之而转,而不及天运一度13],最后说“今坐于地,但知地之不动。”(《朱子语类》卷八十六)[14]朱子的观点(据星湖,这是对“地动”说的否定)亦须深入思考。
进而言之,圣人著述的《易经·乾卦·大象》中有“天行健”之说。据此,由于“圣人无所不知”,因而所谓“天行健”,即指天之自动而不容怀疑,李瀷指出:“可信且从之”。
要之,李瀷以经书的“天行健”一句来驳斥科学命题的“地动”说[15],竭力宣扬当时已成西学定论的“天动”说。
(2)《跋职方外纪》
《星湖全集》卷五十五的《跋职方外纪》,以《中庸》的子思语为根据,主张地圆说的合理性,也提出了同样的论述。《职方外纪》是意大利人耶稣会士艾儒略增译、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1557~1626)所汇编的五卷本世界地理书,完成于明天启三年(1623),收于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另外一人李之藻(1565~1630)编纂的《天学初函·理编》。
李瀷的《跋职方外纪》,开首便引用了《中庸》第26章的“地,振河海而不泄”。[16]李瀷指出,子思的说法(前半部分)意味着,并非海洋在陆地中漂浮,而是陆地纳大海于自身。即便在溟海或渤海之外,海洋必然有底,其底部皆为陆地所构成。这与西洋人详细论证的说法相契合,没有丝毫差异。
大地将海洋收于其中而海水不外泄,这是因为大地处于天圆的中心位置。由于天由东向西一日一周,所以处于天之运转中的物体,势必因其向心力的作用,而不得不向中心集中。即所谓“在天之内者,其势莫不辏以向中”。地既不下坠也不上升,上下四周皆以地为下、以天为上,其原因是一样的。[17]
由海洋是附着于陆地的观点,便不难推出“地圆”的命题。因为若向西航行至极,终究将再次进入东海(所谓“航海穷西,毕竟得出东海”)。而且,如果在航海的途中观察星象,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天顶亦各有差异。因为南界星可以在低纬度看见,而无法在高纬度看见。
《职方外纪》记录了西洋人真实的航海记录。例如其中记录了阁龙(哥伦布)寻找到东方大地(实际是美洲,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墨瓦兰(麦哲伦)由东洋(实际是美洲)到达中国大陆(实际是亚细亚的马鲁古),绕地球一周(卷四“墨瓦蜡尼加总说”)等。了解到麦哲伦环球一周的事实,则“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
李瀷根据子思的话,否定了“天地载水而浮”(张衡《浑天仪》)的传统浑天说/天圆地方说,由此展开论述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但是,李瀷的理论也有含糊之处。因为如果反过来看李瀷的说明,也许以下的说法反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即以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为依据,来揭示《中庸》第26章中的一句话里所隐含的意思,以此否定了传统的浑天说/天圆地方说。《中庸》第26章的这句话只是说“地振河海而不泄”,然而根据李瀷的观点,所谓“地振河海而不泄”就是指“地圆”,这一理论相比“天行健”即“天动”的说法,更是一种强辩而已。
(3)西学优越说
李瀷在进行东西科学理论比较研究之际,虽以实现两者的无矛盾统一、以经学理论为优的融合/折中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并没有将儒学/朱子学作为审视标准而让其发挥强烈作用。当他面对异端的西欧科学理论的绝对优越性之际,他承认传统科学存在缺陷,并向本国的知识人简要说明了西欧科学的内容及其先进性。例如阐释日月蚀发生原因的《日月蚀辨》以及说明东西岁差、南北岁差的《跋天问略》等便是此类著作。
李瀷特别赞赏传到东方的欧洲星历象数之学,主张西欧科学确实优于东亚的传统科学。例如除《日月蚀辨》《跋天问略》等以外,他在《星湖僿说·天地门》的《中西历三元》中指出:“西国之历,中国殆不及也。泰西为最,回回次之。”同样,在《历象》中,他也指出:“今行时宪历,即西洋人汤若望所造。于是乎,历道之极矣。日月交蚀,未有差谬。圣人复生,必从之矣。”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他的西学优越说。另外,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言西学的优越性,但是以其优越性为前提的论述其实也非常多。例如《北极高下说》《论周礼土圭》《地毬》等都是如此。
从西学优越说的立场来看,笼统、含糊地主张东西一致,其实这种主张无非是一方面承认西学的相对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儒学/朱子学当中也有类似之说。在李瀷的科学论当中,西学优越性是默认的逻辑前提,而以李瀷为代表的东亚西学研究者的中西会通论则应理解为这样的理念或思想潮流的结果,即18世纪以来显著的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宏观宇宙论乃至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结果。
二、洪大容的学术
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祖籍为京畿道南阳,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实学家。[18]
(一)燕行与思想革命
洪大容生于朝鲜朝英祖七年(1731),比李瀷大约晚50年。两人不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环境,甚至教育环境都不相同。与李瀷出身南人名门不同,洪大容出身老论世家。另外,洪大容于英祖十八年(1742),有志于“古六艺之学”,列入栗谷李珥→沙溪金长生(1548~1631)→尤庵宋时烈一系的金元行(1702~1772)之门下,属于朝鲜朱子学两大学派——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中的栗谷学派,这意味着他是以李珥为楷模来从事朱子学研究的。
洪大容自英祖三十五年(1759)到三十八年(1762)左右,制作了浑天仪。英祖四十一年(1765),随冬至使节赴中国清朝的京师(燕都)。第二年,访南天主堂,与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会谈,还与杭州读书人严诚、潘庭筠、陆飞进行了学术交流。回国后,提出“应向中国(从北方)学习”(北学)的主张,朴趾源等人也表示认同。英祖五十年(1774),荫补为世孙翊卫司侍直官。后历任泰仁县监、永州郡守等职。正祖七年(1783)去世,享年53岁。
1.洪大容与朱子学
洪大容的实学思想即燕行后的思想,看上去是与朝鲜两班思想不同的价值相对主义,富有批判精神,较诸李瀷更进一步地摆脱了朱子学的束缚,从其规范当中释放出来而获得了自由。但是燕行前,洪大容则完全固执于看似老论领袖宋时烈等人之说的以朱子学为独尊的立场。
例如,根据《湛轩集》外集卷三《乾净衕笔谈》1766年2月23日的记载,洪大容面对王阳明同乡的中国知识人,断然指出:
愚未见陆集,未知其学之浅深,不敢妄论。惟朱子之学,则窃以为中正无偏,真是孔孟正脉。子静如真有差异,则后学之公论,无怪其摈斥。
可见,他对于陆学及阳明学等所采取的似乎不屑一顾的态度。
但是燕行之后,这种孤陋的想法变得隐晦起来。根据《湛轩集》内集卷二《桂坊日记》1775年2月18日的记载,东宫(后来的正祖)对于洪大容思想中不受学统之局限的富有弹性的理气之解表示了赞赏:
桂坊(洪大容)之言甚确,观此言则桂坊似不为固滞之论。[19]这表明洪大容在经历了燕行之后,其思想信念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思想革命
洪大容燕行前后思想信念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要指出其变化的具体内容则并不容易。因此,本文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诗经·小序》与朱子《诗集传》解释的关系,看一看经过与杭州读书人的讨论,洪大容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1
以下的分析意在表明,通过与思想信念不同的浙人笔谈,洪大容对于构成自己思想基础的朱子学产生了一些怀疑。
根据《湛轩集》外集卷二和卷三《乾净衕笔谈》的记载,洪大容与浙人围绕朱子《诗集传》究竟应如何评价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始见于2月8日严诚(字力闇)的记录:
力闇曰:“朱子好背小序。今观小序甚是可遵,故学者不能无疑于朱子。本朝朱竹坨著《经义考》二百卷,亦辟朱子之非是,而自来之论,亦谓朱子好改小序,殆出于门人之手。”
严诚吸收了当时清朝知识人的朱子学批判,主张应当重视《诗经·小序》(诗序),并批评朱子在编撰《诗集传》(修订本,即今本)时,取郑樵之说,以为《小序》为乱经之元凶而将其删除。这是对拘泥于《诗集传》的攻序派而进行的批判。
对此,洪大容于2月10日写了反驳严诚的书信(《与力闇书》):
其破小序拘系之见,因文顺理,活泼释去。……乃其深得乎诗人之意,发前人所未发也。……至若小序之说,则愚亦略见之矣。……全不成文理,此则朱子辨说备矣。盖其踏袭剽窃,强意立言,试依其言而读之,如嚼木头,全无余韵。其自欺而欺人也,亦太甚矣。……若以《集注》谓非朱子手笔而出于门人之手,则去朱子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先辈之世、讲明若烛照,虽为此说者,岂不知其为朱子亲迹,而特以举世尊之,强弱不敌,乃游辞伪尊,软地插木,为阳扶阴抑之术也。
不过,严诚回应2月10日的《与力闇书》是在2月23日。严诚对于洪大容的反驳,仅冷淡地吐露一句:‘《小序》决不可废,朱子于诗注实多蹈驳,不敢从同也。”而且潘庭筠也站在严诚一边,指出:“朱子废《小序》,多本郑渔仲。”此外,陆飞也指出:“老弟宗朱,极是。然废《小序》,必不能强解也。”并在介绍马端临的说法之同时,指出朱子《诗集传》的不足,而且做出如下结论:“鄙意朱子注书甚多,或不无门人手作。”三人的主张都是基于当时新兴的清朝考据学的成果,并无丝毫过激之处,然而洪大容却回应道:“此不可以口舌争。请归而详览诸教。或有妄见,当以奉复也。”表示无法认同这样的主张。
到了2月26日,洪大容用预先准备好的文章来展开自己的观点,不过跟以前的一样,他反复强调:“诗之扫去《小序》,为其最得意处,而大有功于圣门矣。及闻兄辈之论,不觉爽然,而自失矣。”严诚等三人对洪大容的反驳又进行了再反驳,据说是“酬酢颇多”。
但是,论战的结果却是洪大容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失败,向三人表示了自己内心想法的变化:
东国知止有朱注,未知其他。弟之所陈,亦岂敢自以为不易之论耶。至于小序,一读而弃之,不复精究。当于归后,更熟看之。
据《乾净衕笔谈》的记录,论战获得圆满结束,据称“诸人皆有喜色”。
洪大容通过与中国清朝知识人的笔谈,接触到新学问的一角,引发了自己的思想革命,开始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作为自己思想基础的朱子学,尽管只是局部的批判。
这类批判在《毉山问答》一书中有显著的表现。虽然他还奉行老论一系的朱子学,然而另一方面他对朱子学末流之弊表明了对决的姿态,并企图加以改革,此即燕行后洪大容的思想立场。这也就是为何在他的思想主张中,并没有朱子学者常见的那种道学式的固执与独断的毛病。
换言之,持价值相对主义立场的洪大容的思想就是在信奉朱子(宗朱)与批判朱子(攻朱)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基础上而得以成立的。
(二)基本思想
洪大容的基本思想即燕行后的思想与李瀷相同,其特征是在宗朱与攻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若对其思想特征进行归纳的话,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批判形式化、空洞化的朝鲜朱子学,立足于朝鲜的现实,主张实用的实际学问(实学)的必要性;
第二,支持中国清朝的善邻对外开放政策,主张必须积极地吸收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北学);
第三,提出“以天视物”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
1.实学
不过,上列第一的“实学”观,很有可能是受其恩师金元行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是因为根据《湛轩集》内集卷四《祭渼湖金先生文》(1772)的记载,洪大容曾经得到金元行的如下教诲:
问学在实心,施为在实事,以实心做实事,过可寡而业可成。
另外,《湛轩集》外集卷一《答朱郎斋文藻书》(1779)中则提到:
吾儒实学,自来如此。若必开门授徒,排辟异己,阴逞胜心,傲然有惟我独存之意者,近世道学矩度,诚甚可厌。惟其实心实事日踏实地。先有此真实本领,然后凡主敬致知修己治人之术,方有所措置,而不归于虚影。
可见,洪大容的实学观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为了追求真正的朱子学。
2.北学
上列第二的“北学”即主张必须积极地学习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重视清朝文化。洪大容通过自身的燕行经历,将此主张付诸实践。从其实践的事实来看,或许与其个人的资质有很大的关联。例如洪大容学习并掌握了中国语(北京话)的会话,尽管可能并非十分熟练;另外,他与那些从朱子学(名分论)的立场出发而对辫发感到羞耻的汉族知识人也有深入的交流。洪大容所追求的与异民族的宽和交往,其结果正呼应了中国清朝的善邻对外开放政策。批判了基于朝鲜朝老论的朱子学(华夷论)的非现实的清朝敌视政策(北伐论),这就意味着宋时烈所提倡的孤陋狭隘的自尊自大之政策的失败。归国以后,老论主流派的北伐论者(金钟厚等)批评洪大容与清人的交往乃是违反了朱子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交友方式,若从当时两国外交的形势来看,这类批评可以说是必然的反应。
3.以天视物
关于第三点,即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毉山问答》与《林下经纶》当中。其中,洪大容阐发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毉山问答》)
主张人类中心的价值观是不足取的,而构成其“人物均论”的基础则无非是“以天视物”这一观点。所谓人物均论,与其所属的老论、洛论的人物性同论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且不论他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正如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他的人物均论确是受到了人物性同论的影响。
此外,洪大容并没有将“以天视物”设定为人与禽兽草木的本质差别,而是将其价值相对主义观点应用于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理论,其因在于他拥有“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的观点。他的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
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诸侯衰弱,吴楚滑夏,寇贼无厌。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这是主张从华夷论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批判歧视异民族,此即所谓“域外春秋说”。此外,洪大容由这样的观点出发,梦想建立基于能力而没有身份制的万民皆劳的社会(《林下经纶》)。
(三)价值相对主义与西学知识
燕行后的洪大容,就生活在思想与现实或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矛盾纠结中,并在趋向不同的两种张力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可以推断此即洪大容价值相对主义得以形成的缘由。不过,《毉山问答》一书所披露的价值相对主义,并不是消极的、脆弱的,而是充满着倡导实学以及全面否定虚学的毫不动摇的自信。其充满自信的原因在于,他的思想主张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
1.地球说与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
据洪大容的《毉山问答》,若要问人类社会之当为与价值相对主义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何在,则无外乎起源于欧洲的科学知识[21],即地圆说与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这是因为“人物之生,本于天地。”
洪大容认为大地是由球形构成的:
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
另外,他以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为依据,指出:
满天星宿,无非界也。自星界观之,地界亦星也。无量之界,散处空界。惟此地界,巧居正中,无有是理。
这是说,不能将地球看作宇宙的中心(“空界之正中”)。
2.价值相对的社会理想与天地的相对性
洪大容利用西欧的科学知识,揭示了天地的相对性,进而提到了“人物之本”“古今之变”“华夷之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地球也非宇宙的中心。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必要以中华为贵,也没有必要遵从华夷秩序。
毫无疑问,洪大容坚信本国未来遥远的前途、提倡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理想,他的这种心情定能超越时代传达给读者。价值的相对化是必然的。
若对以上所述用命题化的方式做一归纳,那么可以这样说,诱发出洪大容的价值相对主义社会思想,是由于跟中国知识人的真心交流,但是其理论支撑则是传播到东亚的崭新的欧洲数理科学知识。
三、小结
李瀷与洪大容,将倭乱、胡乱之后出现的朱子学相对化推向极致,是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实学家。可以说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将朱子学与西学二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若要对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想的展开做一推断,无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朝鲜实学不仅与朱子学的学统相关,而且他们个人也是发自内心地尊敬朱子的学德,并以李滉或李珥为楷模,来从事朱子学研究。与此同时,又受到朱子学改革主义的影响,或者因燕行而发生思想革命,导致他们开始对朱子学作一番相对化的尝试。而引发相对化的无疑是理义。在尹东奎所撰的《星湖行状》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瀷)如其义安则不规规于人己,理得则不切切于毁誉。勇往直前,不顾傍人是非。”这个说法生动地描绘出李瀷等实学家重视理义的研究态度。无疑,实学家一方面要注意不能大幅度地越出朱子学的架构,另一方面又乐于追随理义而自由地思索。
其次,在追求理义的过程中,他们与西学相遇,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实学的视野。与擅长实用与逻辑的西欧科学的邂逅,其影响尤其之大。实学家经历了由西学东渐而导致的18世纪东亚的宏观宇宙论(cosmology)的转换(变化),并受到西学魅力的影响而开始了真正的西学研究。在西学当中,西欧科学之实用性且又精致的理论,使得这些实学家自觉到自己视野的狭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刺激。通过热心地研究西学,其结果使得实学家步入了新的学问路径以及新的知识世界。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异端持宽容态度的反朱子学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异端,只要其中有可学习之处,便应毫不犹豫地加以学习;也是强调中西会通,即强调经学理论为优的朱子学与实学以及西学之间的理论整合与折中。实学家在西欧科学由微至细的学习(刺激)之下,对传统学风进行修正,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学问构架。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作者单位:日本东京大学,译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校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附注
注释:
[1]李退溪:《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实记》卷1,《增补退溪全书》第4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第16页(下引《增补退溪全书》皆为此本)
[2]李退溪:《论理气》,《退溪全书》卷下,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58年影印本,第702页(下引《退溪全书》皆为此本)
[3]《答南时甫》,《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369页
[4]李退溪:《答李宏仲问目》,《陶山全书》(3),首尔: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0年,第89页上。(下引《陶山全书》皆为此本)
[5]《天命图说》,《陶山全书》(3),第600页下。
[6]《答乔侄问目(中庸)》,《陶山全书》(3),第209页上。
[7]《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陶山全书》(2),第22页上。
[8]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3、35、37页。
[9]《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94,第2370页。
[10]《太极图说辨戾文》,转引自《明儒学案》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1]《答李公浩问目》,《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299页上。
[12]张立文:《李退溪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34、136页。
[13]《答郑子中别纸》,《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17页下~18页上。
[14]《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405页下。
[15]同上书,第420页上。
[16]同上书,第406页下。
[17]参阅尹丝淳的《韩国儒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94~95页。
[18]《答奇明彦第二书》,《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418页上~421页上。
[19]尹丝淳:《韩国儒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20]《圣学十图》,《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203页下。
[21]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53页。
[22]参阅拙著:《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之比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章。
[23]《圣学十图》,《增补退溪全书》第1册,第202页上。
[24]同上书,第203页下。
[25]同上书,第208页上。
[26]同上书,第210页下。
[27]张立文主编:《退溪书节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注释:
[1]李申:《话说太极图》,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3~29页。
[2]李申:《我与周氏太极图研究》、张其成《周敦颐<太极图>考》,两篇均载于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3]这近似于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类的意志既然因为自由之故可以直接受道德法则的决定,因而如果对这个动机功夫纯熟,不加勉强,那么最后也会在主观上产生一种愉快的感情。”“这种快乐,这种自得之乐并不是决定行为的原理,只是意志单受理性直接决定一事才是这种快乐感觉的根源……”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112页。关于儒家的“道义之乐”与康德所说由道德法则决定的“自得之乐”的异同,参见拙文《儒家的“乐”与“忧”》,载《中国儒学》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度正作《周敦颐年谱》有云:“先生遂扶(母)柩厝于龙图公墓侧。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胡文恭诸名士与之游。”
[5]钱穆说:“理学兴起以前,已先有一大批宋儒,此一大批宋儒,早可称为是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8、16页。
[6]参见拙文:《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7]胡瑗《周易口义》卷一云:“盖性者天生之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备具,故禀之为正性。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唯圣人则能使万物得其利,而不失其正者,是能性其情,不使外物迁之也。”
[8] 陆九渊在《与朱元晦》信中说:“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其实,二程不仅不言“无极”,而且不言“太极”。现传《二程集》中《程氏易传》有两篇序,首篇是《易传序》,此序明标“河南程颐正叔序”,又有一篇《易序》,未署名作者,其中有云:“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此《易序》是后人补入,且与朱熹的《周易本义》用了同一篇序。据朱熹弟子熊节编的《性理群书》,此《易序》当为“文公先生”所作。除此之外,《二程集》中都不讲“无极”和“太极”。
[9]如程颢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程氏遗书》卷二上)“‘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不诚则无物也。”(《程氏遗书》卷十一)“‘天地设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盖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则人只于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诚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识而自得之也。”(同上)
[10]《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宋深之一》:“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熹自十四五时得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年,但觉其义之深、指之远。”
[11]朱熹“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与他早年向李侗提出以“太极”为“未发”,以“太极动而生阳”为“已发”有类似之处。
[12]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13]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第182页。
[14]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77页。
[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
注释:
[1]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0~3721页。
[2]同上书,第3808页。
[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96~4600页。
[4]同上书,第4600~4601页。
[5]同上书,第4602页。
[6]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1页。
[7]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01页。
[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09页。
[9]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8页。
[10]同上书,第646页。
[11]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03页。
[12]同上书,第4604页。
[1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14~3815页。
[14]同上书,第3808页。
[15]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2~283页。
[16]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7页。
[17] 同上书,第397~455页。
[1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02页。
[19]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82~783页。
[20 ] 同上书,第788~789页。
[21]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2页。
[22]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第627~699页;李华瑞《宋代仓储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
[2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025页。
[2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1~3722页。
[25]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台北:台北市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47~454页。
[26]常建华:《乾隆朝整饬社仓研究》,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5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
[27]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01页。
[2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79~3780页。
[29] 同上书,第3804页。
[30] 同上书,第3798~3799页。
[31]同上书,第3808~3809页。
[32] 同上书,第3775~3776页。
[33] 同上书,第3815页。
[34]王文书:《宋代借贷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35]《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926页。
[36]《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市籴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十通”影印本,“考”第5173页。
[37] 同上书,“考”第5175页。
[38]《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市籴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十通”影印本,“考”第5177页。
[39] 同上书,“考”第5186页。
[40]《川陕总督岳钟琪奏陈社仓积贮管见折》,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90页。
[41]乾隆《临潼县志》卷4《赋役志·仓储》。
[42]常建华:《乾隆朝整饬社仓研究》,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5辑,第249页。
[43] 同上书,第255页。
[44]以上奏折转引自《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上)》,《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
[45]常建华:《乾隆朝整饬社仓研究》,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5辑,第255~261页。
[46]以上奏折转引自《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下)》,《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
[47]参见《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下),《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
[48]同上。
[49]同上。
[50]《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七《市籴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十通”影印本,“考”第5201页。
[51]以上奏折参见《乾隆朝整饬社仓档案》(下),《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
注释:
[1]张立文:《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2]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26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321页。
[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
[5]王安石:《周官新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1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页。
[6]《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
[7]同上书,第671页。
[8]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63~3264页。
[9]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4~735页。
[10]同上书,第619页。
[11]《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4页。
[12]同上书,第215~216页。
[13]《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0页。
[14]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第1218页。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
[16]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43页。
[17] 同上书,第745页。
[18]《宋史全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0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第372页。
[19]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73~774页。
[20]王安石:《周官新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1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2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页。
[22]《孟子·离娄上》。
[23]《孟子·公孙丑上》。
[24]《孟子·告子下》。
[25]《荀子·天论》。
[26]《韩非子·五蠹》。
[27]《韩非子·和氏》。
[28]《韩非子·奸劫弑臣》。
[29]《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0~451页。
[30]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4页。
[3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14页。
[3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第5334页。
[33]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第61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8页。
[34]《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第10550页。
[35]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4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3页。
[36]《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第613页。
[37] 同上书,第319页。
[38]《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54页。参考文献:
[1]《孟子》《荀子》《韩非子》等。
[2]《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5]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第61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6]《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7]《宋史全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0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8]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9]王安石:《周官新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1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0] 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4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1]张立文:《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3]《四书或问》,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7册(影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4]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注释:
[1]库恩指出,范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群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业绩。(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前言,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野家启一:《库恩:范式》,毕小辉译,陈化北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3]从学术分类上看,学术界更愿意接受汉学与宋学的分别,但从研究范式的视角看,子学范式与经学范式的区分更为有效。先秦是中国哲学的草创阶段,系统性研究还谈不上,但韩非的《解老》《喻老》、庄子的《天下篇》与荀子的《解蔽》《非十二子》的研究范式都应从属于子学研究范式。
[4]这个五步法分别是:(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存》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8年,第233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
[6]同上。
[7]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80~
281页。
[8]同上书,第267页。
[9]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61~162页。
[10]颜炳罡:《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范式转换之得失及未来走向》,《文史哲》,2010年第5期。
[11]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12]西方世界较少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来解读古代哲学史,但哈度(Petre Hadot ) 则将其扩展到古代哲学史研究,他对哲学话语(philosophical discouse )的变 化分析,在《什么是古代哲学》(What is Ancient Pilosophy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13 ]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14]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15]西格弗里德・耶格尔:《对实践话语中批判话语的分析》,参见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福柯的迷宫》,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145页。
[16] “格式塔” Gestalt,指观念或观念系统瞬间发生整体转换。
[17] J.P.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 ory and Method.《话语分析入门:理论与方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18]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0页。
[19]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导言》,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0]朱人求:《道学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以宋代“定性说”的展开为中心》,《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1]在指向社会行动方面,批判性话语分析尤为突出,它的宗旨是揭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22]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74页。
[23]西格弗里德•耶格尔:《对实践话语中批判话语的分析》,参见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编:《福柯的迷宫》,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145页。
[24] J.P.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 Ory and Method.《话语分析入门:理论与方法》,第13页。
[25] Barbara Johnstone.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Black Well.2002.pl52.
[26]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页。
[27]张再林:《对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28]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页。
[29]朱人求:《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方法》,《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30]陈来:《略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1] Swales J.提出了话语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话语共同体确实存在,而且,由一群分散的个体所构成的话语共同体有以下六个特点:(1)一个话语共同体 有一系列普遍一致的公开目的。(2) 一个话语共同体有成员间相互交流的机 制。(3)一个话语共同体利用其内部交流机制,为成员提供信息及其反馈。(4)一个话语共同体具有并使用一种甚至多种文章格式和风格,并以此来推 动交流。(5)一个话语共同体还具有某些特别的词汇。(6) 一个话语共同体 还不断吸收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新成员,保持共同体的旺盛生命力。(参见 Swales, J. 1990 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
Cambridge: CUP.PP24~27.)
[32]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施家炜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第118 ~119页。
注释:
[1]参见拙文:《义理与训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征引原则》,《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第326页。
[2]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第4316页。
[3]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卷170“理宗淳祐元年”,第4630页。
[4]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云:“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 结之。”
[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0《选举二》。
[6]钱穆撰:《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第180~181页。
[7]拙撰:《四书“官学化”进程:〈四书大全〉纂修及其体例》,载《东亚汉学回顾与展望》,长崎:长崎中国学会,2010年,第87~102页。
[8]萧启庆撰《元代科举特色新论》云:“道学在科举中的独尊及成为近世的官学是始于元代,而非宋代。不过,道学在元代仅为儒学各派中的官学,还算不上‘正统’学术。因为科举在当时并非入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学不过是诸‘教’中的一种。道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明朝。”又云:“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及学校教育的准绳,废弃旧注疏不用,但这两部官纂大全与元代科举所用注疏乃是一脉相承。朱学独尊的地位自此获得巩固。”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1分(2010年3月)。
[9]杨士奇等撰《明太宗实录》卷158载:“上谕行在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
[10]侯美珍撰:《明清科举取士“重首场”现象的探讨》,《台大中文学报》,第23期,2005年12月。
[11]邹元标撰:《愿学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5页。
[12]高攀龙撰:《高子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1页。
[13]陆陇其撰:《松阳钞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6页。
[14]皮锡瑞撰:《经学历史》,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98页。
[15] 同上书,第289页。
[16]参见拙文:《〈四书大全〉征引人物系谱分析》,《东吴中文学报》,第23辑,2012年5月。
[1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63《勉斋学案》载全祖望案语云:“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傅,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其人与?”
[18]程继红撰:《宋元朱熹门人及后学籍贯地理分布与朱子学传播区域》,《朱子学刊》,2008年第1辑。
[19]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20]同上。
[21]蔡沈撰《朱文公梦奠记》云:“八日,精舍诸生来问病,先生起坐,曰:‘误诸生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坚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见蔡有鹍辑,蔡重增辑:《蔡氏九儒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6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第793页。
[2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23]何基研读方法,乃是承继黄榦《集注》与《或问》相参方式扩而及于语录的结果。黄榦门人陈宓《论语通释题叙》言:“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盖《集注》之辞简而严,学者未能遽晓,于是作《或问》一书,设为问答,以尽其详,且明去取诸家之意。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辞而列之于后,以便观览。”见《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0页。按:此书今已不传,无法得见黄榦光大师门的成果,然而此一诠释路径,已为后人开启思考方向。
[24]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25]同上。
[26]王柏认为《大学》“格致传”不缺,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听讼”一章,为“格致传”,是受车若水的影响。至于分出《中庸》为两篇,则是受《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的启发。王柏撰:《鲁斋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156页。
[2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黄百家案语云:“后世之宗紫阳者,不能入郛廓,宁守注而背经,而昧其所以为说,苟有一言之异,则以为攻紫阳矣。然则,鲁斋亦攻紫阳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学也!”
[28]柳贯撰:《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待制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8页。
[29]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30]《两朝纲目备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脏腑微利……辛酉改《大学》‘诚意’一章,此熹绝笔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复出书院。”蔡沈撰《朱文公梦奠记》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学》‘诚意’一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午后,大下,随入宅堂,自是不能复出楼下书院矣。”见蔡有鹍辑,蔡重增辑:《蔡氏九儒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6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第793页)。不过钱穆依江永之说,认为朱熹最后所改其实并非《大学》“诚意”章,而是《大学》“诚意”二字最先见处之注,将经一章原本“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中“一于善”改为“必自慊”。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二册,第425页。
[31]黄溍撰:《白云许先生墓志铭》,《文献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2页。
[32]同上。
[33]纪昀撰:《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8页。
[34]廖云仙撰:《元代<四书〉学的继承与开创——以元儒许谦为例》一文,以许谦为例,观察元代《四书》学,其中有继承之一面,也有开创的地方。以朱学为学术核心,阐发朱注,为其继承之处;考订错误,补其缺失,则为其开创的地方。载《东海中文学报》第21期,2009年7月。
[35]阮元撰:《研经室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48页。
[36]王柏撰:《鲁斋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页。
[37] 同上书,第161页。
[38]章一阳辑:《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
[39]戴锜撰:《原序》,见许谦撰《白云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1页。
[40]朱彝尊撰:《经义考》卷254。
[41]吴师道推崇何、王、金、许北山一系学人,乃是元代后期建构北山一系学术地位的重要推手。《吴正传先生文集》中有《请乡学祠金仁山先生》《代请立北山书院文》《请传习许益之先生点书公文》等文章,可以得见其用心所在。至于强调北山一系为朱学嫡传,则是在柳贯为金履祥所写的行状,以及黄溍为许谦所写的墓志铭中逐渐形成的论述内容。参见陈雯怡撰:《“吾婺文献之懿”——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载《新史学》总第20卷第2期,2009年6月。
[4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27页。
[43]宋濂撰:《元史》卷189《儒学列传》。
[44]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47页。
[45]方逢辰撰:《蛟峰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0~545页。
[46]方彦寿撰:《朱熹书院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3页。
[47]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0《告子上》。《宋元学案》卷45《范许诸儒》云:“范浚,字茂明,……学者称为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诵习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朱子语类》卷59云:“问:‘《集注》所载范浚《心铭》,不知范曾从谁学?’曰:‘不曾从人,但他自见得到,说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见吕伯恭甚忽之,问:须取他铭则甚?曰:但见他说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说话,人也多说得到。曰:正为少见有人能说得如此者,此意盖有在也。’”
[48]浙江省武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吕祖谦与浙东明招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26页。
[49]束景南撰:《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15~633页。
[5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51]浙东学术重视文献,也强调文学,乃是地域学术传统。徐永明撰:《婺州文人群体之构成及其形成之地域文化背景》,《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52]参见拙著:《“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第19~21页。
[53]邓文原撰:《四书通序》,胡炳文撰:《四书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54]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志铭》,陈栎撰:《定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1~442页。
[55]程瞳撰:《新安学系录序》云:“新安为程子之所从出,朱子之阙里也。故邦之人于程子则私淑之,有得其传者;于朱子则友之事之,上下议论,讲劘问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时以还,硕儒迭兴,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寿其传。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贤贤相承,绳绳相继,而未尝泯也。盖朱子之没,海内学士群起著书,争奇衒异,各立门户,浸失其真。诸先哲秉相传之正印,起而闲之。故笔躬行之实,心得之妙,乃于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究极精微,阐明幽奥,朱子之所未发者,扩充之;有畔于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焕然于天下。我太宗皇帝诏修《五经》《四书》《性理》……一惟其言是宗。采录之以明圣经,淑人心,维民极,而垂教后世,则其有功于圣道正学大矣哉!”见《新安学系录》,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56]参见拙文:《四书“官学化”进程:〈四书大全〉纂修及其体例》,《东亚汉学回顾与展望》,第87~102页。
[57]胡炳文撰:《四书通证序》,《云峰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2页。
[5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2。
[59]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68页。
[60]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2774页。
[61]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70页。
[62]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461页。
[63]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84页。
[64]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2765页。
[65]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2100页。
[66]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26页。
[67] 同上书,第325页。
[68]详见拙著:《“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第197~209页。
[69]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52~53页。
[70] 同上书,第51~52页。
[71]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序》,《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18页。
[72]胡广等纂修:《读中庸法》引黄榦云:“《中庸》自是难看,石氏所集诸家说,尤乱杂未易晓,须是胸中有权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骤取而读之,精神已先为所乱,却不若子细将《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晓,俟首尾该贯后,却取而观之可也。《中庸》与他书不同,如《论语》是一章说一事,《大学》亦然。《中庸》则大片段,须是滚读,方知首尾,然后逐段解释,则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滚读,以《章句》仔细一一玩味,然后首尾贯通。”见《四书大全》,第320页。
[73]胡广等纂修:《读中庸法》,《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23页。
[7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
[75]胡广等纂修:《中庸或问》,《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626页。
[76]胡广等纂修:《中庸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405页。
[77] 同上书,第381页。
[78] 同上书,第520~521页。
[79] 同上书,第515页。
[80] 同上书,第516页。
[81] 同上书,第517页。
[8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5。
[83]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序》,《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15页。
[84]胡广等纂修:《大学章句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49~50页。
[85]胡广等纂修:《孟子集注大全》,《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041页。
[86]胡广举荐42位儒士一同参与纂修,核其职衔,乃是以翰林院统合朝中各部郎中、主事,以及地方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等,层面既广,人数又多,与唐代《五经正义》由学官而及于朝廷大员的纂修过程有所不同。明代结合中央与地方,既是成祖综纳四方的统治手段,也是朱熹后学深化传播的影响所致。核查地域,江西籍有胡广、金幼孜、萧时中、陈循、周述、余学夔、涂顺、吴嘉静、周忱、王选、王复原、傅舟、杜观、颜敬守、彭子斐、吴余庆等16人,福建籍有杨荣、陈全、林志、李贞、陈景著、黄寿生、陈用、黄约仲、洪顺、陈道潜、黄福、王暹等12人,浙江籍有陈璲、王羽、童谟、吴福、沈升、章敞、吾绅、曾振、留季安、宋琰、陈敬宗、许敬轩等12人。其他,刘永清是湖广人,王琏、赵友同、陈济是江苏人,黄裳是广东人,段民是直隶人,杨勉是应天府人,廖思敬、刘三吾是湖南人。显然,人员集中于江西、福建、浙江三地。江西、福建、浙江正是朱熹学术流扇之地,修纂人员与此相符,而江西、福建人数远高于浙江,用意所在,可以想见。参见拙撰:《四书“官学化”进程:〈四书大全〉纂修及其体例》,《东亚汉学回顾与展望》,第89页。
注释:
[1]以上朝鲜思想史的概述,基于川原秀城:《朝鲜思想大观》,《斯文》第123号,2013年。
[2]所谓“实学”或“朝鲜实学”,并非是存在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确定的历史概念,而是后世历史学家为便于解释当时状况而设定的概念。从实学的思想性格来看,形成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实学观,各种实学观各自主张自己的正当性,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本文分析的特点是,以对西学的接受为视角来考察朝鲜朝的实学,即以朱子学与西学在朝鲜的会通和融合来定义实学。
[3]有关李瀷,笔者曾有3篇论文发表,即《星湖心学——朝鲜王朝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与亚里士多德的心论》(《星湖心学——朝鮮王朝の四端七情理气の辨とアリストテレスの心論》,《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6集,2004年),《李瀷的科学思想》(《李瀷の科学思想》,《星湖学报》第8号,2010年),《李瀷的科学论与朱子学的相对化》(《李澳の科学論と朱子学の相対化》。该文曾于2013年“星湖先生逝世250周年纪念学术会议”上发表)。
[4]关于李瀷思想的概况,可参见 Kimyongge [ 김용걸 ]《星湖李澳》( 韩国人物儒学史编撰委员会《韩国人物儒学史》, hangirsa [한길사], 1976年)、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东明社,1987年)、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史》(亚细亚文化社,1995 )、李相益《实学的学派成长——星湖李澳》(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韩国 实学思想史》, 图书出版 daunsim [ 다운샘 ],2000年 ) 等。
[5]有关李瀷的性理学,可参见张志渊:《朝鲜儒学渊源》(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与《星湖全集》文集附录卷一等。
[6]金光来之东京大学博士论文:《星湖心学形成的研究——坚守与自得的折中与西学》,《星湖心学形成の研究—堅守と自得の折衷そして西学—》,未刊, 2015年。
[7]金光来:《中世基督教灵魂论的朝鲜朱子学之变容:耶稣会的适应主义与星湖的心性论》(《中世キリスト教霊魂論の朝鮮朱子学的变容:イエズス会の適应主義と星湖の心性論》),《死生学研究》13号,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 系研究科,2010年。
[8]有关李瀷的天文数学内容,可参见朴星来《星湖イ塞説속의西洋科学》(《震檀学报》第59号,1985年)、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一志社,1986年)等。
[9]据《星湖僿说类选·技艺门》的算学,李瀷引用徐光启之说:“徐光启有言曰:‘算学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盖欲心思细密而已。’此说极是。”强调作为学术理论与实用技术之基础的算学的作用。但是,徐光启的话引自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中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杂议》,确切而言,并没有说到一般算学有如此的重要性。原文为:“此书(《几何原本》)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这不过是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做出的评价。李瀷将算学作为学问的基础予以很高的评价,这并不仅仅是援引而已,而是高度抽象化后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命题。按星湖的直觉,他将西欧文明的本质之一的数学所重视的逻辑思维很好地纳入自己的视野中。
[10]四端七情论是代表朝鲜朱子学的重要理论。张志渊在《朝鲜儒学渊源》中指出:“吾东儒教性理之学,自丽季郑圃隐(郑梦周,1337~1392)始倡,而历数百年……其遗言微旨,多不传于世。唯退陶(李滉)先生深究性理之源,始有四七理气之发明,而于是诸家异同之论起矣。”所谓四端七情论,“四端”指人所具备的道德情感。《孟子·公孙丑上》中所说“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礼之端”的“辞让之心”和“智之端”的“是非之心”。“七情”指《礼记·礼运》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的特征都是“不学而能”的。
[11]蔡济恭所撰《墓碣铭》(《星湖全书》文集附录卷一)就此问题指出:李瀷“患退翁以后,四七理气之说,与朱子所解‘道心发于义理,人心发于形气’,《语类》所载‘四理、七气’有所抵牾,撰《四七新编》,发挥朱子之旨,羽翼退陶之说。”(译者按,退翁、退陶,均指李滉)
[12]李瀷将自己的四端七情论说成是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的转化,然而实质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论。因此我们不得不高度评价李瀷的才华。
[13]《星湖僿说·天随地转》中指出:“朱子曰:‘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其意若曰:‘天一日一转,地随而转,不及天一度也。’这是天地两动说。
[14]《朱子语类》卷八十六载“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李瀷的引用,则将语句倒了过来,无疑地朱子认为“天与地俱转”。但是,对于朱子的天地两动说,李瀷指出“天与地俱转,地亦坠下矣”,以此证明朱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15]《易经疾书》就《乾卦·大象》中的说法,指出:“地圆九万里,一日一周,已是难矣。”明确否定地动说。
[16]《中庸章句》注曰:“振,收也。”
[17]李瀷亦指出,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但近海而不往下流注,北海未尝干涸,南海未尝增益,这是因为海洋都处于地之上而且皆以天为上的缘故。
[18]本部分原为川原秀城:《朝鲜数学史——朱子学的展开及其终结》(《朝鮮数学史——朱子学的な展開とその終焉ー》),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4章“3洪大容の价值相对主义”中有关朱子学与社会思想的论述,在此略做补充。关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亦可参见此书。
[19]问答如下:“令曰:‘然。性理最难言。吾意果主于不相离,而乃云兼知觉为性,则不免语病矣。若理气先后,当云何如?’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则是气先理后否?春坊或言气先,或言理先。臣曰:理气先后,自来儒者各有主见,而若《中庸》注说,亦非谓成形而后理乃赋焉。臣则以为有则俱有,本不可分先后。盖天下无无理之物,非物则理亦无依着也。’笑令曰:‘其言甚好。如是看最无弊。’顾春坊而再三称之。臣曰:‘此非臣之创见,即朱子说也。’令曰:‘虽然,理气说虽讲之烂熳,于身心日用,终未见切实。’臣曰:‘睿教甚当。日用当行之事,切问而近思,随事体行,则性理亦非别物,即散在于日用。及其知行并进,则一原大本,性与天道,可以豁然贯通。初学之坐谈性命,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令曰:‘此言极是。以子贡之颖悟,晚年始闻性道,则初学尽不可躐等。桂坊之言甚当。。观此言则桂坊似不为固滞之论。’”
[20]洪大容燕行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与耶稣会传教士鲍友菅的笔谈。耶稣会士引起的思想革命,详见川原秀城:《朝鲜数学史——朱子学的展开及其终结》。
[21]洪大容先于他人吸收了西欧科学知识并应用于自己的社会思想,但是其科学理论本身基本没有独创性的见解。朴星来在《洪大容〈湛轩书〉中的西方科学之发现》一文中指出“严格地说,他的主张几乎没有独创性”(韩国《震壇学报》79,1995年)。
参考文献:
[1]《庄子》《韩非子》《墨子》《管子》《孟子》《周易》。
[2]王充:《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3]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4]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7]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0]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1]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2]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13]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4]《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5]邓国光:《经学义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6]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7]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8]陈寅恪:《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9]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20]吕祖谦:《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21]孙甫:《唐史论断序》,《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2]韩愈:《韩昌黎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23]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24]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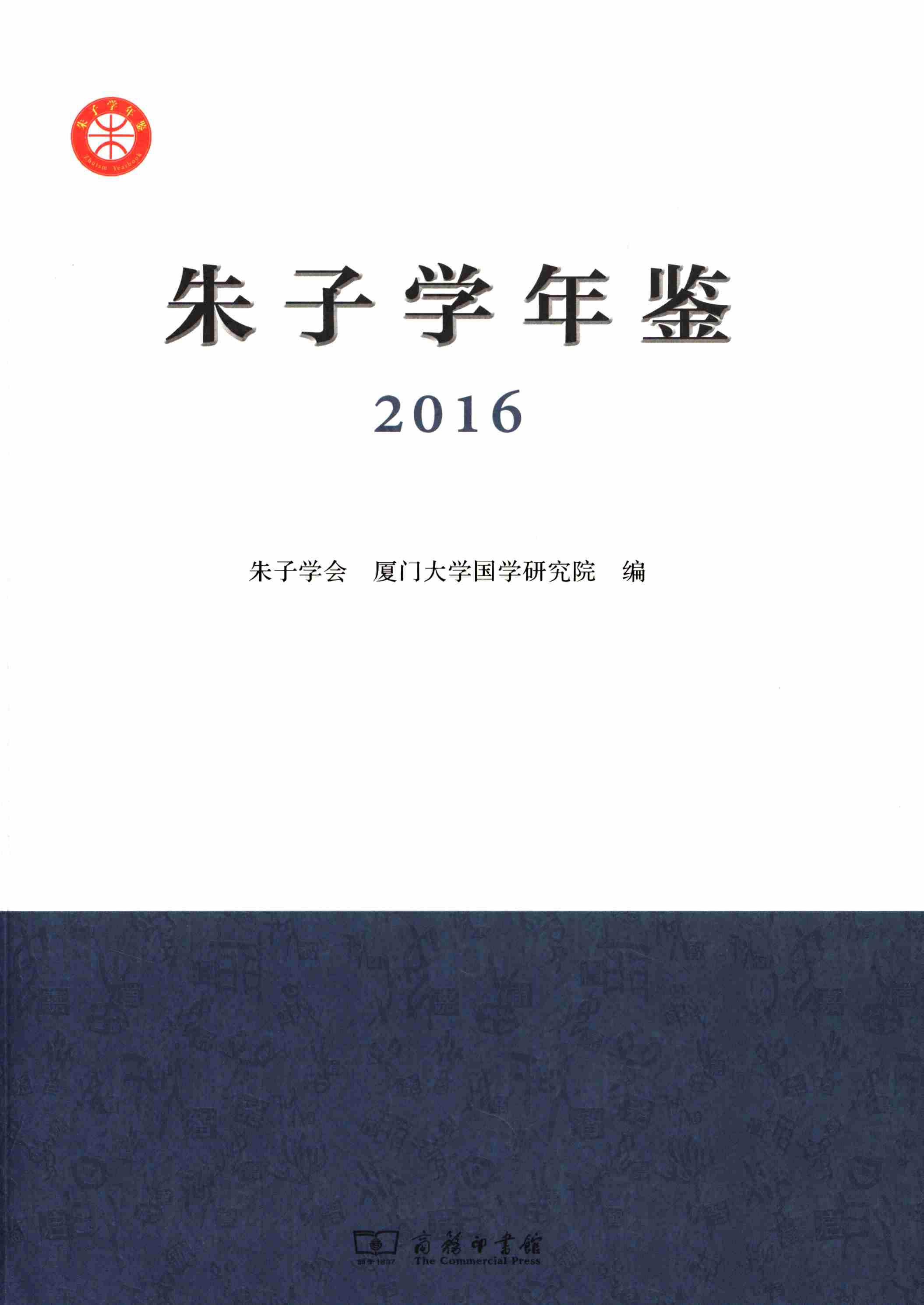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