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6》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272 |
| 颗粒名称: | 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2 |
| 页码: | 002-01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的《克斋记》是与他的《仁说》同时完成的主要作品之一。朱子在43岁时初次写下了《克斋记》,并在44岁时进行了修订。该作品是朱子中年仁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克斋记》的创作年代可以追溯到乾道八年(壬辰年,即公元1192年),当时朱子是43岁。 |
| 关键词: | 朱子 2016 《克斋记》 |
内容
朱子的《克斋记》,是与他的《仁说》同时完成的主要作品,初写于43岁,改定于44岁。《克斋记》与《仁说》同为朱子中年仁学思想的代表作。
乾道八年壬辰,朱子43岁,为友人石子重作《克斋记》,而早在四年前,朱子39岁时,其答石子重书已经提到:克斋恐非熹所敢记者,必欲得之,少假岁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见稍复有进,始敢承命耳。1当时石子重居家待次,以克名斋,这显然是用了《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他请朱子为他作克斋之记,申发对孔子“克己复礼”的理解,而朱子回复他说要等几年所见有了进步,才敢承命。
一、《克斋记》先本通行本《朱子文集》中《克斋记》文本之末有朱子自署“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谨记”,也就是说,在四年之后即乾道八年,朱子终于为石子重写下了《克斋记》。所以《克斋记》的著作年代,向无争议。[2但《克斋记》从初稿到定稿,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以往少有研究。让我们先来看《朱子文集》所载的朱子《答石子重第十一书》,以下所录此书,左顶格加下划线者为朱子的批语,退格的段落是石子重的问目:“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是为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爱亲从兄之心习而察,则仁矣。然而不敢说必无犯上作乱,故曰“鲜”。其或有之,以其习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为仁,患在不察故尔。《表记》曰:“事君,处其位,不履其事,则乱也。”谓违君命为乱。此所谓“犯上”者,犯颜作乱者,违命也。
孝弟,顺德;犯上作乱,逆德。论孝弟却说犯上作乱底事,只为是它唤作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一般。君子则不然,先理会个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许顺之云:“ ‘其为人也孝弟’,犹是泛而论之。如君子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与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务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顺德,终是不善之心鲜矣。”此二说,大抵求之过矣。“鲜”只是少。圣贤之言,大概宽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说杀了。此章且看伊川说,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恕也。”又《语录》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正解此两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恕也,近于仁矣,然未至于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为仁,后以为恕而未仁,二义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为未仁,则“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二先生说经,如此不同处亦多,或是时有先后,或是差舛,当以义理隐度而取舍之。如此说,则当以《解》为正,盖其义理最长,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与“欲无加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详之。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明曰:“动容貌,周旋中礼,暴慢斯远;正颜色则不妄,斯近道曰:“动容貌,周旋中礼,暴慢斯远;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此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远暴慢、斯近信、远鄙倍,犹云便远暴慢、便近信、便远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辞气之出,不使至于鄙倍。”却是就“远”字上用工。上蔡云:“动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处。”又曰:“紧要在上三字。”说不同,如何?熹详此意,当以明道之说为正。上蔡之说尤有病。
《克斋记》说“天下归仁”处,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后本云:“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先后意甚异,毕竟“天下归仁”当如何说?初意伊川说,后觉未稳,改之如此,乃吕博士说。恐当以后说为正。盖所谓伊川说,亦止见于《外书·杂说》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子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支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更乞开发。
此义近与湖南诸公论之,甚详,今略录一二上呈,亦可见大意矣(一答胡广仲书“仁”之说,一答张敬夫书)。3]此书前面主要讨论《论语》及二程对《论语》的解释,后面提到《克斋记》,应是《克斋记》作成后非久,当作于乾道壬辰本年,朱子43岁。
据上引石子重与朱子书所问,《克斋记》有“先本”和“后本”之别,其中提法颇有不同,可以看到朱子写作和修改的过程。盖朱子写成《克斋记》后,即寄给石子重,不久后又觉其中有未安处,故再寄修改稿给石子重。据朱子自述,其先本主张“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是以伊川之说为主,后本则主张“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中”和克己说,是以吕大临之说为主。这说明朱子此篇《克斋记》文在初稿后又曾经修改。石子重看到过两个稿本,而今存本《克斋记》中朱子这里所提及的两句都没有踪影,可知《朱子文集》中的《克斋记》,既不是石子重书中所说的“先本”,也不是“后本”,应是后来最终改定的定本。
上引石子重与朱子书指出:《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仔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肢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4]石子重的说法是欲调和知觉言仁说和以爱推仁说两者,可见石子重认为《克斋记》是朱子与湖南学者关于知觉言仁辩论的后续部分,是承接知觉言仁论辩的。朱子批云:“此义近与湖南诸公论之甚详,今录一二上呈,亦可见大意矣。一答胡广仲书,一答张敬夫书。”[5]事实上,《克斋记》没有特别强调爱,只是说到“恻隐之心无不通”,“感而遂通,而无一物之不被其爱”,但熟悉当时仁论说的石子重很敏感地发现,朱子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知觉言仁”的话语。朱子则明白点出,这确实是与湖南诸公的知觉论辩有关,故把他和湖南学者张栻、胡广仲论知觉言仁的两封书信转给石子重参阅。朱子说的“此义”应当是指对知觉言仁的辨析。朱子《答胡广仲书》并未谈及《克斋记》,也未提到《仁说》,故《答胡广仲书》应略早于《克斋记》。
石子重得书后放弃了知觉言仁说,回报曰:“所疑荷批诲,今皆已释然,盖仁者心有知觉,谓知觉为人则不可,知觉却属智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朱子答云:“仁字之说甚善,要之,须将仁义礼智皆作一处看。”[6]朱子与石子重的论《克斋记》的几通书信,都是以论仁为主题,且提到仁字之说,但都没有提到朱子写的《仁说》,而《仁说》也是集中论仁,可见作《克斋记》时还未有《仁说》。若当时已有《仁说》,以朱子与石子重的关系而言,朱子必然寄给石子重共商讨论。既然二人都未提及《仁说》,由此可推知写作《克斋记》时尚未有《仁说》。尤其是石子重说《克斋记》“似以爱之说为主”,显然是还没有见到过《仁说》,因为《仁说》正是强调以爱论仁、以爱推仁。故《克斋记》与《仁说》虽然都是朱子43岁时的作品,但《克斋记》在前,《仁说》在后。《克斋记》是此前知觉言仁之辩的延续(又见《语类》陈淳录),而《仁说》则是对仁的全面讨论。
《朱子文集》中提到《克斋记》还有数处,如朱子《游诚之一》答:《克斋记》近复改定,今别写去。后面不欲深诋近世之失,“波动危迫”等语,皆已削去。但前所论性情脉络、功夫次第,自亦可见底里,不待尽言而后喻也。因见南轩,试更以此意质之,当有以相发明尔。[7]游诚之也是湖南学者。朱子在此书中提到了几处对《克斋记》的具体删修意见。其关键是,不再批评程门后学的错误理解(即所谓近世之失),而保留性情论和工夫论的论述。今存《克斋记》定本,其修改后的面貌与朱子这里所说完全一致。
《朱子文集》别集卷六《答林择之十一》:《尤溪学记》及《克斋记》近复改定,及改去岁《仁说》《答钦夫》。
数书本欲写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钦夫《语解》去,看毕寄还,并论其说。[8]此书作在乾道癸巳,朱子44岁。此书说到“克斋记近复改定”,当在一时先后。有学者认为这里只讲“去岁仁说”,没有说《克斋记》是去岁所作,似表明《克斋记》作在《仁说》之后。其实,因此时石子重到任尤溪县令,特请林择之来县学教学,又请朱子为作尤溪学记,所以朱子与书先提到与尤溪和石子重有关的二文,而后提到《仁说》等。
朱子答张栻“又论仁说”书:来教云:“夫其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蕴,人与物所公共,所谓爱之理也。”熹详此数句,似颇未安。盖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则于其所当爱者又有所不爱。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矣。若爱之理,则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后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说》,其间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来教以为不如克斋之云是也,然于此却有所未察。窃谓莫若将“公”字与“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后却看中间两字相近处之为亲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谓以公便为仁之失。此毫厘间,正当子细也。又看“仁”字,当并“义礼智”字看,然后界限分明,见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所以多说而易差也。又谓“体用一源,内外一致”为仁之妙,此亦未安。盖义之有羞恶,礼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内外一致,非独仁为然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9]主张仁是爱之理,是朱子知觉言仁之辩中强调的重点。[10]已有学者见此书引述张栻认为仁说不如《克斋记》,从而推论仁说在《克斋记》之前,其实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此书是论《仁说》,而不是论《克斋记》;观其中辞意,作此书时,朱子方欲修改《仁说》而尚未动手。
而张栻则在评朱子《仁说》之前,已经看到过《克斋记》,故其评语中有《仁说》不如《克斋记》的文字。从这里并不能得出《克斋记》在《仁说》之后的结论。
《朱子语类》只有一处提及《克斋记》:问:“程门以知觉言仁,《克斋记》乃不取,何也?”曰:“仁离爱不得。上蔡诸公不把爱做仁,他见伊川言:‘博爱非仁也,仁是性,爱是情。’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惜门人只领那意,便专以知觉言之,于爱之说,若将浼焉,遂蹉过仁地位去说,将仁更无安顿处。‘见孺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处见得亲切。圣贤言仁,皆从这处说。”又问:“知觉亦有生意。”曰:“固是。将知觉说来冷了。觉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边。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须自看得,便都理会得。”(淳。寓同。)[11陈淳所录在朱子守漳州时,已在绍熙初。但朱子门人仍然注意此文,而且陈淳明确指出《克斋记》是针对“知觉言仁”而发的,这与《克斋记》写成时石子重的感觉是一致的。
二、《克斋记》后本如上所说,朱子《克斋记》有先本、后本、改定本。先本今已失传,但后本仍保存未失,此即宋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中的《克斋记》。此本文集乃淳熙末年朱子在世时刊行,但并不是朱子自己刊行的。南宋末以来八百余年间,历代学者从未提及此本文集,因为此本文集不是朱子刊行的,故其中所收的文章颇多是朱子的初稿,而非定稿,弥足珍贵。
此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今藏于台北故宫,20世纪80年代影印出版。
[12]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中的《克斋记》即是朱子与石子重问答书中所谓后本,全文录之如下(加下划线者为与文集定本之异,在定本中已经被删去):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浑育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然则人之求之,亦岂在夫外哉?特去其害此者而已矣。
盖所谓仁者,天理之公也;所以害仁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分而相为消长,彼既盛则此不得不衰矣。故求仁者克去己私,以还天理,至于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视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焉。默而存之,固蔼然其若春阳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有感而遂通,则无一事之不顺于理,而无一物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德所以尽情性之妙也欤。
昔者颜子问仁于孔子,而孔子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告之。
其于用力于仁之要,可谓一言而举矣。至于近世,程氏之学,祖述孔颜,尤以求仁为先务,而其所论求之之术,亦未有以易此者也。
吾友会稽石君子重,盖闻程氏之说而悦之者也,间尝以克名斋,而讯其说于予。予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工也。。今子重择于斯言而有取于克之云者,则其于所以用力于仁之要,又可谓知其要矣,尚奚以予言为哉!继今以往,如将因夫所知之要而尽其力,至于造次颠沛之顷而无或怠焉,则夫所谓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于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为哉!虽然,自程门之士有以知觉言仁而深疾夫爱之说者,于是学者乃始相与求之于危迫之中而行之于波(流)动之域,甚者扬眉瞬目,自以为仁,而实盖未尝知夫仁之为味也。予惧子重之未能无疑于其说也,则书予之所闻者如此以复焉。使吾子重无骇于彼而有以安于此,则斯言也于辅仁之义其庶几乎。年月日记此文的意义是保存了《克斋记》早期的面貌,虽然石子重所说的最初的先本已经看不到了,但淳熙本文集保存了后本即第一次修改本,还是很珍贵的。从中可以参证《克斋记》初稿写成以后的修改变化。后本的思想要点是,人的本心是来自天地之心的仁,仁义礼智是未发,恻隐羞恶是已发,仁之体发为恻隐之用。人欲之私,所以害仁,故求仁必克去己私,这就是“克己复礼”。而持久的克己最后可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气象,这就是“天下归仁”。
后本对先本修改的关键是对《论语》“天下归仁”的理解,如石子重说:“《克斋记》说‘天下归仁’处,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后本云:“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先后意甚异,毕竟“天下归仁”当如何说?”朱子解释说:“初意伊川说,后觉未稳,改之如此,乃吕博士说。恐当以后说为正。盖所谓伊川说,亦止见于《外书·杂说》中,容或未必然也。”就是说,先本对“天下归仁”的解说是用程伊川的说法,后本的修改则采用了吕大临的说法。朱子解释说,后本之所以放弃了伊川说,既是因为吕大临说在义理上为妥当,也是因为伊川的说法只是见于《外书·杂说》,材料不太可靠。不过,从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保留的后本来看,后本中对吕大临说的采用并不是直接接在论及“天下归仁”的语句后,而是置于“至于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纯”的表述之后。这与石子重所说略有不同。
总之,在求仁的工夫论上,《克斋记》后本强调以克己言仁,不赞成以知觉言仁,其最后一段对程门上蔡等的知觉言仁说及其实践弊病,给予了直接的尖锐批评。特别是所谓“甚者扬眉瞬目,自以为仁”,虽然没有指明是何人及为何如此,考虑到朱子后来亦以此严厉批评陆象山门人,足见朱子对程门后学知觉言仁之实践的不满。可惜,这最后一段在定本中复被删去,使《克斋记》本来针对知觉言仁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被遮掩了。
三、《克斋记》定本后世《朱子文集》中的《克斋记》即《克斋记己》的定本。定本强化了天理人欲之辩,在天下归仁的解释上去掉了北宋的解释,也不再直接批评程氏门人,但在性情之德、天地所以生物之心问题上未变。其文如下(加下划线者为后本所无,乃癸巳所改定):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
然人有是身,则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无害夫仁。人既不仁,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益无所不至。此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盖非礼而视,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听,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言且动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于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感而通焉,则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尽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则夫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可谓一言而举也与。然自圣贤既远,此学不传,及程氏两先生出,而后学者始得复闻其说,顾有志焉者或寡矣。
若吾友会稽石君子重,则闻其说而有志焉者也,故尝以克名斋,而属予记之。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今子重择于斯言,而独以克名其室,则其于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谓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为哉!自今以往,必将因夫所知之要而尽其力,至于造次颠沛之顷,而无或怠焉,则夫所谓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于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为哉!顾其所以见属之勤,有不可以终无言者,因备论其本末而书以遗之,幸其朝夕见诸屋壁之间,而丕忘其所有事焉者,则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尔。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谨记。[13此文的明显修改之处,一个是文章的后面去除了后本原有的最后一大段,不再批评程门弟子与知觉言仁的弊病;一个是前面改写了人欲害仁而克己的必要,但也去掉了程门弟子吕大临的视天下说。而义理最核心的第一段没有做任何改变。
据石子重与朱子书,《克斋记》先本主张“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的伊川之说,后本则主张“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中”的吕大临一体言仁之说。这说明一体言仁说还不是朱子《克斋记》开始写作时反思程门的重点。但今存本此两句皆无,可知朱子此篇记文应在《仁说》之辩后修改,把涉及程门的地方都删去了。朱子答湖南学派学者游诚之(南轩门人)书云:“谢先生虽喜以觉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觉,而不言知觉此心也。请推此以验之,所谓得失,自可见矣。若以名义言之,则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界分脉晓,自不相关。但仁统四德,故人仁则无不觉耳。然谢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谓不仁者无所知觉则可,便以心有知觉为仁则不可’。此言亦有味,请试思之。《克斋记》近复改定,今别写去。后面不欲深诋近世之失,‘流动’‘危迫’等语皆已削去。”淳熙本《克斋记》中有“视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焉”,又有“求之于危迫之中而行之于波(流)动之域”,可见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的《克斋记》正是所谓后本。朱子所谓“克斋记近复改定”,正是指将此后本再加改正删修,成为后来通行本《朱子文集》所载的《克斋记》文本。而朱子定本对后本所修改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删去了对程门后学以知觉言仁的比较严厉的批评词语。
另一较大修改是,后本作“至于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视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焉。默而存之,固蔼然其若春阳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定本改作“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去除了吕大临一体言仁的说法,代之以天地生物之心,从而与文章首段强调仁是天地生物之心的主旨更加吻合。
最后一点,定本比后本增加了一大段,即从“然人有是身”到“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一段。朱子强调人有身则有欲,有欲则害仁,故君子求仁必去欲,做到非礼勿视听言动,这是克己的根本工夫。能克之不已,就可以恢复胸中的天地生物之仁心。这一段突出了天理和人欲的冲突,把求仁克己归结为存天理去人欲,并且在后面一段中又强调,认为求仁之要就是要明了“天理人欲相为消长”。这些都是后本中所没有的。
《克斋记》的大意是:仁是人心,来自天地的生物之心,人的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体现了仁的体用之妙,而克己是求仁之要,这些与《仁说》是一致的。《克斋记》定本“粹然天地生物之心”的讲法,仍然有着湖南学派的印记,盖五峰《知言》有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全具。”[14]朱子中年以前用语,多受《知言》影响,湖南学派对早年朱子影响之大,由此亦可见矣。但朱子用“生物”讲天地之心,这是朱子与湖南学派的不同,也明显是对湖南仁说的补充和改造。[15]
四、与《仁说》之比较为了比较参照《克斋记》有关天地之心等思想和词句,我们把朱子《仁说》的文字也列于下方: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
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逊、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口央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
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
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之说,不亦误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谓爱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则彼皆非欤?曰: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则可见矣,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觉之云者,于圣门所示乐山能守之气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因并记其语,作《仁说》。16]因本文并不是对《仁说》的研究,故这里只着重讨论《克斋记》与《仁说》的比较。朱子《仁说》亦几经修改,于乾道癸巳年定稿,《朱子文集》所收《仁说》即是定稿。把《克斋记》定本与《仁说》定本二者加以比较可见,其中思想基本一致,但侧重不同,《仁说》更为全面地阐发了朱子的仁学思想:第一,《仁说》反复以爱言仁、以爱推仁,并以此与北宋以来各种仁论相区别,而《克斋记》后本、定本都只有一处涉及爱,可以说《克斋记》完全没有突出以爱言仁。这一差别非常明显。第二,《克斋记》后本曾用程氏门人吕大临的物我一体为仁的说法,《克斋记》定本则完全删除了这一说法,也不再涉及其他程门弟子后学,而《仁说》则不仅保留了吕大临之说,并指出了此说的局限。《克斋记》先本、后本都曾明确针对程门后学知觉言仁说的弊病加以批评,而《克斋记》定本中删去了对知觉言仁说的提及和批评,但《仁说》中明确表达了对知觉言仁说及其弊病的批评,并引用了程颐“觉不可以训仁”而彻底否定了知觉言仁说。这就使得对程门仁论的反思完整体现在《仁说》,而丝毫不见于《克斋记》,《克斋记》定本只是从天道和工:夫正面论述了克己复礼的思想。这也是《克斋记》与《仁说》的重大不同。可以推测,《克斋记》初稿本是明确针对程门知觉言仁的,但后来在《仁说》中全面表达了对程门论仁的批评,所以《克斋记》的最后修订本就没有必要再保留对程门知觉言仁的批评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察见《克斋记》与《仁说》的先后。第三三,《克斋记》后本、定本在天地之心上的用法是“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仁说》用的是“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子与张南轩辩论仁说中,张南轩反复质疑“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而朱子始终坚持“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最后张南轩也同意了朱子的提法。
考虑到这一点,则《克斋记》没有用“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这只能解释为《克斋记》之作本在《仁说》之前,其文重点不在于此处,后来也就没有必要再加修改了。
另外,还可指出,《克斋记》后本、定本中虽然都肯定地宣称“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但文章首出的是“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两句则在后面。这与《仁说》一上来就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显然有所差别。虽然,二者都认为性情之仁来自天心之仁,但相比之下,《克斋记》更强调仁的性情论,而仁说更突出仁的天道论,轻重先后之间有所差别。当然,这不是思想的不同,而应当是《克斋记》与《仁说》两者的文章功能不同。朱子大概在写作《仁说》之后意识到,《克斋记》既是为石子重所写的斋记,应只突出克己工夫,自然就没有必要像《仁说》那样全面地从天道到性情到工夫到程门弊病进行综合论述了。而所有这一切,必须把《克斋记》前后本之间、《克斋记》与《仁说》之间详加比勘,才可能深入其中,如果我们只就通行本《克斋记》文而观之,是无法了解的。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乾道八年壬辰,朱子43岁,为友人石子重作《克斋记》,而早在四年前,朱子39岁时,其答石子重书已经提到:克斋恐非熹所敢记者,必欲得之,少假岁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见稍复有进,始敢承命耳。1当时石子重居家待次,以克名斋,这显然是用了《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他请朱子为他作克斋之记,申发对孔子“克己复礼”的理解,而朱子回复他说要等几年所见有了进步,才敢承命。
一、《克斋记》先本通行本《朱子文集》中《克斋记》文本之末有朱子自署“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谨记”,也就是说,在四年之后即乾道八年,朱子终于为石子重写下了《克斋记》。所以《克斋记》的著作年代,向无争议。[2但《克斋记》从初稿到定稿,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以往少有研究。让我们先来看《朱子文集》所载的朱子《答石子重第十一书》,以下所录此书,左顶格加下划线者为朱子的批语,退格的段落是石子重的问目:“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是为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爱亲从兄之心习而察,则仁矣。然而不敢说必无犯上作乱,故曰“鲜”。其或有之,以其习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为仁,患在不察故尔。《表记》曰:“事君,处其位,不履其事,则乱也。”谓违君命为乱。此所谓“犯上”者,犯颜作乱者,违命也。
孝弟,顺德;犯上作乱,逆德。论孝弟却说犯上作乱底事,只为是它唤作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一般。君子则不然,先理会个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许顺之云:“ ‘其为人也孝弟’,犹是泛而论之。如君子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与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务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顺德,终是不善之心鲜矣。”此二说,大抵求之过矣。“鲜”只是少。圣贤之言,大概宽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说杀了。此章且看伊川说,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恕也。”又《语录》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正解此两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恕也,近于仁矣,然未至于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为仁,后以为恕而未仁,二义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为未仁,则“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二先生说经,如此不同处亦多,或是时有先后,或是差舛,当以义理隐度而取舍之。如此说,则当以《解》为正,盖其义理最长,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与“欲无加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详之。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明曰:“动容貌,周旋中礼,暴慢斯远;正颜色则不妄,斯近道曰:“动容貌,周旋中礼,暴慢斯远;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此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远暴慢、斯近信、远鄙倍,犹云便远暴慢、便近信、便远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辞气之出,不使至于鄙倍。”却是就“远”字上用工。上蔡云:“动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处。”又曰:“紧要在上三字。”说不同,如何?熹详此意,当以明道之说为正。上蔡之说尤有病。
《克斋记》说“天下归仁”处,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后本云:“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先后意甚异,毕竟“天下归仁”当如何说?初意伊川说,后觉未稳,改之如此,乃吕博士说。恐当以后说为正。盖所谓伊川说,亦止见于《外书·杂说》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子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支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更乞开发。
此义近与湖南诸公论之,甚详,今略录一二上呈,亦可见大意矣(一答胡广仲书“仁”之说,一答张敬夫书)。3]此书前面主要讨论《论语》及二程对《论语》的解释,后面提到《克斋记》,应是《克斋记》作成后非久,当作于乾道壬辰本年,朱子43岁。
据上引石子重与朱子书所问,《克斋记》有“先本”和“后本”之别,其中提法颇有不同,可以看到朱子写作和修改的过程。盖朱子写成《克斋记》后,即寄给石子重,不久后又觉其中有未安处,故再寄修改稿给石子重。据朱子自述,其先本主张“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是以伊川之说为主,后本则主张“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中”和克己说,是以吕大临之说为主。这说明朱子此篇《克斋记》文在初稿后又曾经修改。石子重看到过两个稿本,而今存本《克斋记》中朱子这里所提及的两句都没有踪影,可知《朱子文集》中的《克斋记》,既不是石子重书中所说的“先本”,也不是“后本”,应是后来最终改定的定本。
上引石子重与朱子书指出:《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仔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肢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4]石子重的说法是欲调和知觉言仁说和以爱推仁说两者,可见石子重认为《克斋记》是朱子与湖南学者关于知觉言仁辩论的后续部分,是承接知觉言仁论辩的。朱子批云:“此义近与湖南诸公论之甚详,今录一二上呈,亦可见大意矣。一答胡广仲书,一答张敬夫书。”[5]事实上,《克斋记》没有特别强调爱,只是说到“恻隐之心无不通”,“感而遂通,而无一物之不被其爱”,但熟悉当时仁论说的石子重很敏感地发现,朱子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知觉言仁”的话语。朱子则明白点出,这确实是与湖南诸公的知觉论辩有关,故把他和湖南学者张栻、胡广仲论知觉言仁的两封书信转给石子重参阅。朱子说的“此义”应当是指对知觉言仁的辨析。朱子《答胡广仲书》并未谈及《克斋记》,也未提到《仁说》,故《答胡广仲书》应略早于《克斋记》。
石子重得书后放弃了知觉言仁说,回报曰:“所疑荷批诲,今皆已释然,盖仁者心有知觉,谓知觉为人则不可,知觉却属智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朱子答云:“仁字之说甚善,要之,须将仁义礼智皆作一处看。”[6]朱子与石子重的论《克斋记》的几通书信,都是以论仁为主题,且提到仁字之说,但都没有提到朱子写的《仁说》,而《仁说》也是集中论仁,可见作《克斋记》时还未有《仁说》。若当时已有《仁说》,以朱子与石子重的关系而言,朱子必然寄给石子重共商讨论。既然二人都未提及《仁说》,由此可推知写作《克斋记》时尚未有《仁说》。尤其是石子重说《克斋记》“似以爱之说为主”,显然是还没有见到过《仁说》,因为《仁说》正是强调以爱论仁、以爱推仁。故《克斋记》与《仁说》虽然都是朱子43岁时的作品,但《克斋记》在前,《仁说》在后。《克斋记》是此前知觉言仁之辩的延续(又见《语类》陈淳录),而《仁说》则是对仁的全面讨论。
《朱子文集》中提到《克斋记》还有数处,如朱子《游诚之一》答:《克斋记》近复改定,今别写去。后面不欲深诋近世之失,“波动危迫”等语,皆已削去。但前所论性情脉络、功夫次第,自亦可见底里,不待尽言而后喻也。因见南轩,试更以此意质之,当有以相发明尔。[7]游诚之也是湖南学者。朱子在此书中提到了几处对《克斋记》的具体删修意见。其关键是,不再批评程门后学的错误理解(即所谓近世之失),而保留性情论和工夫论的论述。今存《克斋记》定本,其修改后的面貌与朱子这里所说完全一致。
《朱子文集》别集卷六《答林择之十一》:《尤溪学记》及《克斋记》近复改定,及改去岁《仁说》《答钦夫》。
数书本欲写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钦夫《语解》去,看毕寄还,并论其说。[8]此书作在乾道癸巳,朱子44岁。此书说到“克斋记近复改定”,当在一时先后。有学者认为这里只讲“去岁仁说”,没有说《克斋记》是去岁所作,似表明《克斋记》作在《仁说》之后。其实,因此时石子重到任尤溪县令,特请林择之来县学教学,又请朱子为作尤溪学记,所以朱子与书先提到与尤溪和石子重有关的二文,而后提到《仁说》等。
朱子答张栻“又论仁说”书:来教云:“夫其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蕴,人与物所公共,所谓爱之理也。”熹详此数句,似颇未安。盖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则于其所当爱者又有所不爱。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矣。若爱之理,则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后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说》,其间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来教以为不如克斋之云是也,然于此却有所未察。窃谓莫若将“公”字与“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后却看中间两字相近处之为亲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谓以公便为仁之失。此毫厘间,正当子细也。又看“仁”字,当并“义礼智”字看,然后界限分明,见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所以多说而易差也。又谓“体用一源,内外一致”为仁之妙,此亦未安。盖义之有羞恶,礼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内外一致,非独仁为然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9]主张仁是爱之理,是朱子知觉言仁之辩中强调的重点。[10]已有学者见此书引述张栻认为仁说不如《克斋记》,从而推论仁说在《克斋记》之前,其实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此书是论《仁说》,而不是论《克斋记》;观其中辞意,作此书时,朱子方欲修改《仁说》而尚未动手。
而张栻则在评朱子《仁说》之前,已经看到过《克斋记》,故其评语中有《仁说》不如《克斋记》的文字。从这里并不能得出《克斋记》在《仁说》之后的结论。
《朱子语类》只有一处提及《克斋记》:问:“程门以知觉言仁,《克斋记》乃不取,何也?”曰:“仁离爱不得。上蔡诸公不把爱做仁,他见伊川言:‘博爱非仁也,仁是性,爱是情。’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惜门人只领那意,便专以知觉言之,于爱之说,若将浼焉,遂蹉过仁地位去说,将仁更无安顿处。‘见孺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处见得亲切。圣贤言仁,皆从这处说。”又问:“知觉亦有生意。”曰:“固是。将知觉说来冷了。觉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边。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须自看得,便都理会得。”(淳。寓同。)[11陈淳所录在朱子守漳州时,已在绍熙初。但朱子门人仍然注意此文,而且陈淳明确指出《克斋记》是针对“知觉言仁”而发的,这与《克斋记》写成时石子重的感觉是一致的。
二、《克斋记》后本如上所说,朱子《克斋记》有先本、后本、改定本。先本今已失传,但后本仍保存未失,此即宋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中的《克斋记》。此本文集乃淳熙末年朱子在世时刊行,但并不是朱子自己刊行的。南宋末以来八百余年间,历代学者从未提及此本文集,因为此本文集不是朱子刊行的,故其中所收的文章颇多是朱子的初稿,而非定稿,弥足珍贵。
此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今藏于台北故宫,20世纪80年代影印出版。
[12]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中的《克斋记》即是朱子与石子重问答书中所谓后本,全文录之如下(加下划线者为与文集定本之异,在定本中已经被删去):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浑育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然则人之求之,亦岂在夫外哉?特去其害此者而已矣。
盖所谓仁者,天理之公也;所以害仁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分而相为消长,彼既盛则此不得不衰矣。故求仁者克去己私,以还天理,至于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视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焉。默而存之,固蔼然其若春阳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有感而遂通,则无一事之不顺于理,而无一物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德所以尽情性之妙也欤。
昔者颜子问仁于孔子,而孔子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告之。
其于用力于仁之要,可谓一言而举矣。至于近世,程氏之学,祖述孔颜,尤以求仁为先务,而其所论求之之术,亦未有以易此者也。
吾友会稽石君子重,盖闻程氏之说而悦之者也,间尝以克名斋,而讯其说于予。予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谓复礼之工也。。今子重择于斯言而有取于克之云者,则其于所以用力于仁之要,又可谓知其要矣,尚奚以予言为哉!继今以往,如将因夫所知之要而尽其力,至于造次颠沛之顷而无或怠焉,则夫所谓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于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为哉!虽然,自程门之士有以知觉言仁而深疾夫爱之说者,于是学者乃始相与求之于危迫之中而行之于波(流)动之域,甚者扬眉瞬目,自以为仁,而实盖未尝知夫仁之为味也。予惧子重之未能无疑于其说也,则书予之所闻者如此以复焉。使吾子重无骇于彼而有以安于此,则斯言也于辅仁之义其庶几乎。年月日记此文的意义是保存了《克斋记》早期的面貌,虽然石子重所说的最初的先本已经看不到了,但淳熙本文集保存了后本即第一次修改本,还是很珍贵的。从中可以参证《克斋记》初稿写成以后的修改变化。后本的思想要点是,人的本心是来自天地之心的仁,仁义礼智是未发,恻隐羞恶是已发,仁之体发为恻隐之用。人欲之私,所以害仁,故求仁必克去己私,这就是“克己复礼”。而持久的克己最后可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气象,这就是“天下归仁”。
后本对先本修改的关键是对《论语》“天下归仁”的理解,如石子重说:“《克斋记》说‘天下归仁’处,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后本云:“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先后意甚异,毕竟“天下归仁”当如何说?”朱子解释说:“初意伊川说,后觉未稳,改之如此,乃吕博士说。恐当以后说为正。盖所谓伊川说,亦止见于《外书·杂说》中,容或未必然也。”就是说,先本对“天下归仁”的解说是用程伊川的说法,后本的修改则采用了吕大临的说法。朱子解释说,后本之所以放弃了伊川说,既是因为吕大临说在义理上为妥当,也是因为伊川的说法只是见于《外书·杂说》,材料不太可靠。不过,从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保留的后本来看,后本中对吕大临说的采用并不是直接接在论及“天下归仁”的语句后,而是置于“至于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纯”的表述之后。这与石子重所说略有不同。
总之,在求仁的工夫论上,《克斋记》后本强调以克己言仁,不赞成以知觉言仁,其最后一段对程门上蔡等的知觉言仁说及其实践弊病,给予了直接的尖锐批评。特别是所谓“甚者扬眉瞬目,自以为仁”,虽然没有指明是何人及为何如此,考虑到朱子后来亦以此严厉批评陆象山门人,足见朱子对程门后学知觉言仁之实践的不满。可惜,这最后一段在定本中复被删去,使《克斋记》本来针对知觉言仁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被遮掩了。
三、《克斋记》定本后世《朱子文集》中的《克斋记》即《克斋记己》的定本。定本强化了天理人欲之辩,在天下归仁的解释上去掉了北宋的解释,也不再直接批评程氏门人,但在性情之德、天地所以生物之心问题上未变。其文如下(加下划线者为后本所无,乃癸巳所改定):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
然人有是身,则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无害夫仁。人既不仁,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益无所不至。此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盖非礼而视,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听,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言且动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于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感而通焉,则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尽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则夫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可谓一言而举也与。然自圣贤既远,此学不传,及程氏两先生出,而后学者始得复闻其说,顾有志焉者或寡矣。
若吾友会稽石君子重,则闻其说而有志焉者也,故尝以克名斋,而属予记之。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今子重择于斯言,而独以克名其室,则其于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谓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为哉!自今以往,必将因夫所知之要而尽其力,至于造次颠沛之顷,而无或怠焉,则夫所谓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于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为哉!顾其所以见属之勤,有不可以终无言者,因备论其本末而书以遗之,幸其朝夕见诸屋壁之间,而丕忘其所有事焉者,则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尔。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谨记。[13此文的明显修改之处,一个是文章的后面去除了后本原有的最后一大段,不再批评程门弟子与知觉言仁的弊病;一个是前面改写了人欲害仁而克己的必要,但也去掉了程门弟子吕大临的视天下说。而义理最核心的第一段没有做任何改变。
据石子重与朱子书,《克斋记》先本主张“天下之人亦将无不以仁归之”的伊川之说,后本则主张“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中”的吕大临一体言仁之说。这说明一体言仁说还不是朱子《克斋记》开始写作时反思程门的重点。但今存本此两句皆无,可知朱子此篇记文应在《仁说》之辩后修改,把涉及程门的地方都删去了。朱子答湖南学派学者游诚之(南轩门人)书云:“谢先生虽喜以觉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觉,而不言知觉此心也。请推此以验之,所谓得失,自可见矣。若以名义言之,则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界分脉晓,自不相关。但仁统四德,故人仁则无不觉耳。然谢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谓不仁者无所知觉则可,便以心有知觉为仁则不可’。此言亦有味,请试思之。《克斋记》近复改定,今别写去。后面不欲深诋近世之失,‘流动’‘危迫’等语皆已削去。”淳熙本《克斋记》中有“视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焉”,又有“求之于危迫之中而行之于波(流)动之域”,可见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的《克斋记》正是所谓后本。朱子所谓“克斋记近复改定”,正是指将此后本再加改正删修,成为后来通行本《朱子文集》所载的《克斋记》文本。而朱子定本对后本所修改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删去了对程门后学以知觉言仁的比较严厉的批评词语。
另一较大修改是,后本作“至于一旦廓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视天下盖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之中焉。默而存之,固蔼然其若春阳之温也,泛然其若醴酒之醇也。”定本改作“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去除了吕大临一体言仁的说法,代之以天地生物之心,从而与文章首段强调仁是天地生物之心的主旨更加吻合。
最后一点,定本比后本增加了一大段,即从“然人有是身”到“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一段。朱子强调人有身则有欲,有欲则害仁,故君子求仁必去欲,做到非礼勿视听言动,这是克己的根本工夫。能克之不已,就可以恢复胸中的天地生物之仁心。这一段突出了天理和人欲的冲突,把求仁克己归结为存天理去人欲,并且在后面一段中又强调,认为求仁之要就是要明了“天理人欲相为消长”。这些都是后本中所没有的。
《克斋记》的大意是:仁是人心,来自天地的生物之心,人的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体现了仁的体用之妙,而克己是求仁之要,这些与《仁说》是一致的。《克斋记》定本“粹然天地生物之心”的讲法,仍然有着湖南学派的印记,盖五峰《知言》有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全具。”[14]朱子中年以前用语,多受《知言》影响,湖南学派对早年朱子影响之大,由此亦可见矣。但朱子用“生物”讲天地之心,这是朱子与湖南学派的不同,也明显是对湖南仁说的补充和改造。[15]
四、与《仁说》之比较为了比较参照《克斋记》有关天地之心等思想和词句,我们把朱子《仁说》的文字也列于下方: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
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逊、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口央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
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
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之说,不亦误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谓爱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则彼皆非欤?曰: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则可见矣,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觉之云者,于圣门所示乐山能守之气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因并记其语,作《仁说》。16]因本文并不是对《仁说》的研究,故这里只着重讨论《克斋记》与《仁说》的比较。朱子《仁说》亦几经修改,于乾道癸巳年定稿,《朱子文集》所收《仁说》即是定稿。把《克斋记》定本与《仁说》定本二者加以比较可见,其中思想基本一致,但侧重不同,《仁说》更为全面地阐发了朱子的仁学思想:第一,《仁说》反复以爱言仁、以爱推仁,并以此与北宋以来各种仁论相区别,而《克斋记》后本、定本都只有一处涉及爱,可以说《克斋记》完全没有突出以爱言仁。这一差别非常明显。第二,《克斋记》后本曾用程氏门人吕大临的物我一体为仁的说法,《克斋记》定本则完全删除了这一说法,也不再涉及其他程门弟子后学,而《仁说》则不仅保留了吕大临之说,并指出了此说的局限。《克斋记》先本、后本都曾明确针对程门后学知觉言仁说的弊病加以批评,而《克斋记》定本中删去了对知觉言仁说的提及和批评,但《仁说》中明确表达了对知觉言仁说及其弊病的批评,并引用了程颐“觉不可以训仁”而彻底否定了知觉言仁说。这就使得对程门仁论的反思完整体现在《仁说》,而丝毫不见于《克斋记》,《克斋记》定本只是从天道和工:夫正面论述了克己复礼的思想。这也是《克斋记》与《仁说》的重大不同。可以推测,《克斋记》初稿本是明确针对程门知觉言仁的,但后来在《仁说》中全面表达了对程门论仁的批评,所以《克斋记》的最后修订本就没有必要再保留对程门知觉言仁的批评了。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察见《克斋记》与《仁说》的先后。第三三,《克斋记》后本、定本在天地之心上的用法是“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仁说》用的是“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子与张南轩辩论仁说中,张南轩反复质疑“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而朱子始终坚持“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最后张南轩也同意了朱子的提法。
考虑到这一点,则《克斋记》没有用“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这只能解释为《克斋记》之作本在《仁说》之前,其文重点不在于此处,后来也就没有必要再加修改了。
另外,还可指出,《克斋记》后本、定本中虽然都肯定地宣称“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但文章首出的是“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两句则在后面。这与《仁说》一上来就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显然有所差别。虽然,二者都认为性情之仁来自天心之仁,但相比之下,《克斋记》更强调仁的性情论,而仁说更突出仁的天道论,轻重先后之间有所差别。当然,这不是思想的不同,而应当是《克斋记》与《仁说》两者的文章功能不同。朱子大概在写作《仁说》之后意识到,《克斋记》既是为石子重所写的斋记,应只突出克己工夫,自然就没有必要像《仁说》那样全面地从天道到性情到工夫到程门弊病进行综合论述了。而所有这一切,必须把《克斋记》前后本之间、《克斋记》与《仁说》之间详加比勘,才可能深入其中,如果我们只就通行本《克斋记》文而观之,是无法了解的。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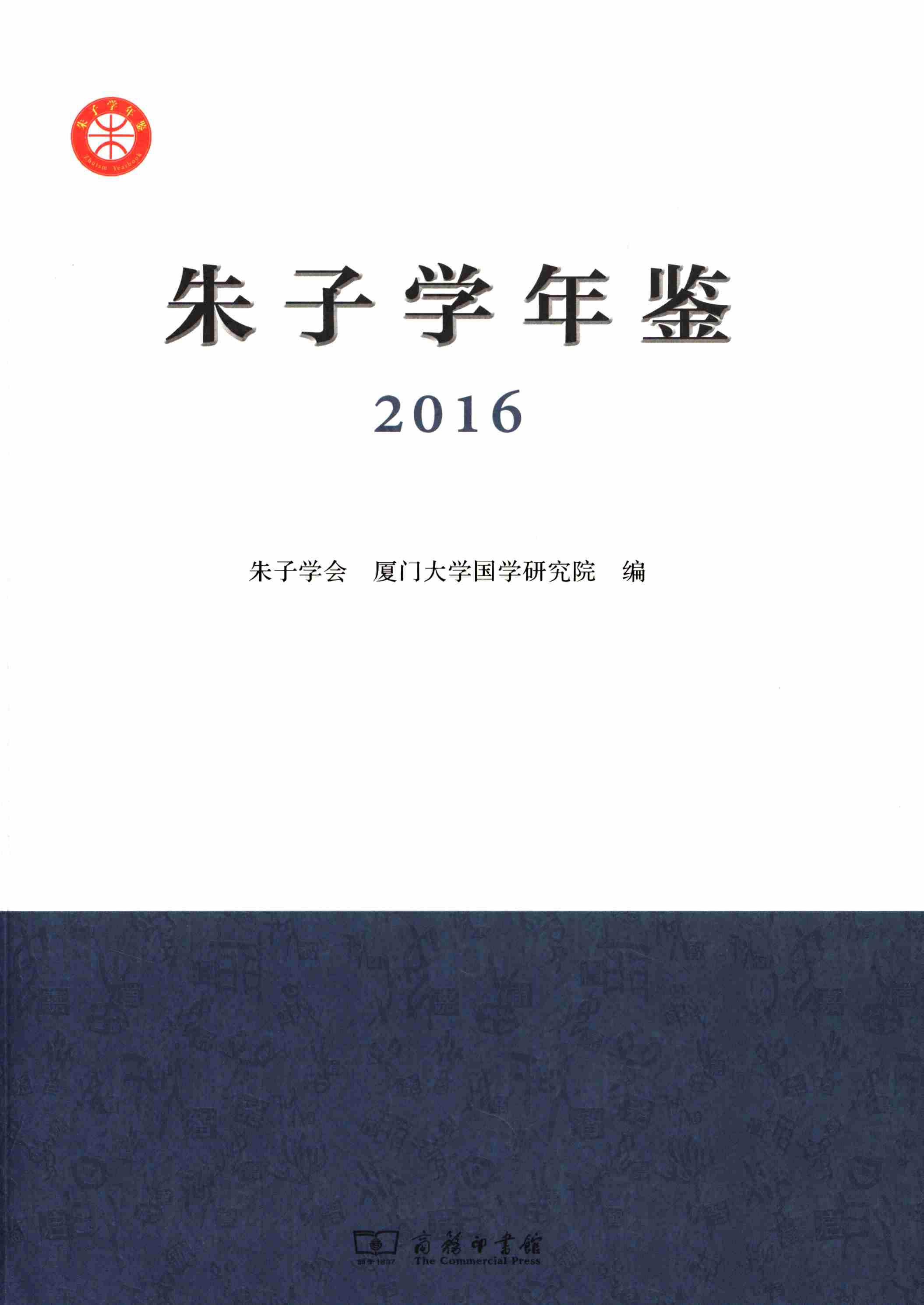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6》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年鉴内容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9个栏目。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来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