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浦朱子祠遐想
| 内容出处: | 《山水襟怀——走近朱子》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163 |
| 颗粒名称: | 竹浦朱子祠遐想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9 |
| 页码: | 50-58 |
| 摘要: | 本文章介绍了琅岐岛上的朱子祠经过修缮,保留了历史特色并增加了新的文化元素,成为当地文化景点和游客参观的地方,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
| 关键词: | 文学作品 朱子祠 琅岐岛 |
内容
不大的琅岐岛,有一座面积不小的朱子祠。
《琅岐岛风采》一书(杨东汉著)对这座祠有这样的描述:“朱子祠始建年间已无从查考。据吴庄林有贵先生说,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林家美,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创建朱子祠,为首总理。以祠为文人雅士燕集之所,以振琅岐之文风。”该书还介绍说,朱子祠“四面烽火山墙,面宽约14米,纵深40米,四扇三间,三落透后,土木结构。头进天井、回廊古朴,中进为三开间,中为厅,旁两厢房,为文人读书之处,后进天井回廊,逐级升高,为朱子殿堂,中央奉祀朱子塑像”。
与很多类似的文化古迹的命运相比,琅岐的这座位于九龙山南麓一个叫竹浦的地方的朱子祠,算是幸运的。它曾经作为书院供学子读书,后来成了生产队办公场所,之后很长时间成了无人问津的旧屋。前年春节,我找到了这个地方,因年久失修,祠的好几根梁柱已被蛀虫侵蚀,有的已经落地歪躺在一旁,墙体也是斑驳陆离的,墙帽上的野草在冬日寒风里萋萋摇摆,一副疲惫模样。万幸的是,主体建筑没有坍塌。再看看岛上重修的多处寺院,香火缭绕,人声鼎沸。我为儒学,为朱文公扼腕长叹,也为人们对历史人文的漠视感到莫名的悲凉。
我不由地想到了古田县杉洋镇。当地的蓝田书院始建于唐代,朱子曾在书院学习、讲学,也因斗争在此避难过,并撰有《东斋记》。其题的“蓝田书院”四个大字,八百多年后依然熠熠生辉。虽然书院不幸于1975年12月在一场大火中烧毁,但2012年,当地乡贤余博士出资三百多万元重修了蓝田书院,并雇请一名教师在书院里为乡人普及国学知识。今天,杉洋人自豪地在镇中心位置立石勒记:“杉洋——朱熹过化之乡”!
琅岐岛上的朱子祠,何时也能焕发风采?
一番上下急切呼吁之后,省区市三级文物部门终于决定,对琅岐朱子祠进行修缮,并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保障。文物专家还叮嘱,祠有明代时期建筑的特点,应当认真保护修复。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近年来党和政府强调文化自信,强调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加大对文物保护的力度,已经有了一定实质性的效果。当我对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在表示祝贺之时也露出了惊讶的眼神,一座不大的海岛,还会有这等规模的朱子祠?为了回答朋友们的疑问,我开始关注起竹浦朱子祠的由来。
朱子祠,是祭祀朱子的场所。朱子,字晦翁,是孔孟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构建了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丰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宋至今,朱子理学不仅影响了中国八百多年,更成了东亚文化的核心内容。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二者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者堪与伦比。”著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这样判断:“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但朱子的一生不是都顺风顺水,到了晚年,还真可谓充满了坎坷。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朱子志同道合的好友赵汝愚被罢去宰相,朝政大权落入心怀野心的韩侘胄一帮手中。于是,凡是与韩侂胄意见不合的,都被称为“道学之人”。不久,道学又被斥责为“伪学”,四书、六经也都成了禁书。再不久,宁宗赵扩又下了诏,订立了所谓的“伪学逆党籍”,史称“庆元党禁”,名列其间者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朱子被斥为“伪学魁首”,名列黑名单第五,所列罪状多达十项,甚至有人提出,要“斩朱熹以绝伪学”。这一年,朱子66岁,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朱子依然讲学不辍,著述不断,也有史料记载,如《福建通志》:“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而在《长乐县志》《古田县志》《霞浦县志》《闽清县志》中,则都有朱子在当地避难寓居的信息。
朱子在闽江口有活动的足迹?这样的历史文字信息让我兴奋。盛夏里的一天,我与朋友一起来到了据说与朱子有着渊源的德成岩。德成岩坐落在今长乐市潭头镇西侧素有“洞天幽绝”之称的筹峰山中。它是福建历史上首位思想家唐代林慎思与其兄进思、景思等筑“月楼精舍”读书的地方。据长乐志记载,宋庆元元年(1195年),朱子避伪学之难寓居长乐时,曾来此凭吊,非常感佩林慎思的“儒英忠义”与“续孟功业”,谓其“德成于此”,于是将“月楼精舍”改为了“德成精舍”。朱子手迹“德成精舍”四个大字至今还镌刻在岩壁上,而岩壁下的泉水,也依然活泼、清冽无比。
21世纪初,为了展示这一文化骄傲,长乐市聚民力进行重修。因缺乏必要的引导与监督,老百姓在德成岩前新修建了一座阁楼,计划作为寺院。后经交涉,同意改为林慎思纪念馆,因为没有经济效益,民间也就缺乏了积极性,阁楼成了半拉子工程。站在现场,大家淌着汗水感慨不已。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长乐潭头镇二刘村的龙峰山上,寻找朱子当年在这里的“讲学处”。当年,村人刘砥、刘砺两兄弟跟从朱子在山上学习,后来,兄弟俩都中了进士。为感念朱子,便将这个地方改名为“晦翁岩”了。到了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率船队驻泊长乐太平港,曾在山上修建了一座龙峰书院。书院掩映在奇岩古树之间,环境清幽,空气清新,有“小洞天”之誉,也是福州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
走进山门,几块岩石耸立,构成了一处天然的幽荫之所。洞外千姿百态的太极榕、盘岩榕、红榕、油杉、罗汉松、红枫等树木遮云蔽日,洞内凉风习习,石凳、石桌、白鹿石雕、酷似两支如椽大笔贴着岩壁耸立而上的树干以及明代郑世威勒刻的“读书处”三个大字,无一不在努力还原着当年朱子与二刘在这里教学相长的情景。山外风雨正紧,洞内书声如故。就是在“禁伪学、除逆党”这样四处腥风的日子里,朱子依然为了理学而忙碌着,看得出,他的心里是如何的坦然与磊落!
我想起曾拜访过的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书院坐落在庐山的南麓山涧中,幽深、古朴。书院始建于唐朝,朱子知南康军(今九江星子县)时,力主重修了书院,并且为书院立下了学规。现在大家熟悉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朱子当年在白鹿洞书院立下的。白鹿洞书院里还真有一个白鹿洞,洞里也有一头白鹿石雕,栩栩如生。
龙峰书院原来是祀朱子和刘砥、刘砺的,后改称三贤祠。三贤祠在21世纪初也经过整修,基本上保持了明代风格。可惜,祠修复后,只是简单地委托给了同在一个山头的寺院管理。同行的二刘村人介绍说,寺院香火旺盛,面积越来越大,而三贤祠却因缺少资金、缺少关注,许多梁柱已经出现了白蚁,如不抓紧处理,三贤祠的倒塌只是个时间问题。我随手敲了敲,很多梁柱确实发出了“噗噗”的中空声。
龙峰书院对面的马尾亭江镇长安村和长柄村,也都有朱子的遗迹。于是,大家离开了晦翁岩,驱车上了琅岐大桥,经过琅岐岛,再开上闽江琅岐大桥,下了桥,不远处就是长安村。我们来到了一个叫西岩寺的地方。
寺院不很规则,但面积不小。最让人称奇的是,一个大堂里摆满了各路神仙菩萨。当地人说,这就是儒道佛的“和平共处”,也算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当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带路人领着我们穿过几个走廊,到了后院一处石壁前。石壁上刻着“仙苑”两个大字,楷书,每字高0.59米、宽0.53米左右,边上草署“晦翁书”,每字径约5.2厘米。
环顾四周,满目都是俗物,一点都体会不到身居仙苑的感觉,更无法体验朱子当年写下这两字时的心情。长安村就面临着闽江,是闽江入海口的一个重要渡口所在。古时候,坐在这里,泡上一壶茶,捧起一卷书,可以观白帆点点,迎清风拂面,对朱子来说,这里不是仙苑又是什么?今天,村里盖起了新楼,江水自然望不见了,“仙苑”两个大字也只能成了人们想象过去的引子。
隔着长安村的,叫长柄村,村里藏着一座福州地区目前规制最大的朱子祠。长柄朱子祠又名龙津书院,由门楼、大殿、文昌阁、后天井等组成,两边置风火墙,占地面积五百多平方米。朱子当年曾在此讲过学,当地人梁汝昌、郑庸斋等从之游,最后也都有了不小的成就。朱子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亭江举人董应举、郭复之等建造的,用来祭祀朱子及弟子梁汝昌、郑庸斋的。今天,祠内还保存着朱子题刻的“跃龙津”三字,门墙内壁嵌有明代董应举《建紫阳先生祠题词》、清代王有树《龙津书院祀典记》等碑刻。朱子祠刚刚经过修复,还散发着油漆香,让人心生快意。
我回望刚才经过的琅岐岛,岛上为什么会有朱子祠的答案似乎也一下子找到了。潭头的二刘村、亭江的长安村、长柄村,它们分别位于闽江的南岸和北岸,大约在一条直线上。不要说是水路舟楫古代,就是在今天,朱子要想过往这两个分别位于闽江南北岸的村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经过琅岐岛。于是,一个大胆的推理跳上心头,朱子曾经到过琅岐岛!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发现而击掌。
当时朱子是和什么人一起经过的?经过时有人知晓吗?为什么地方史志上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也许,南宋时,琅岐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岛,朱子避伪学之祸,出行也不可能大张旗鼓。虽然是悄悄地,但还是有人记住了,于是,才有了之后小岛的文明与开化?
我在更多的史料里读到了这样的信息。这座竹浦朱子祠,实际上也是一座书院,因为坐落在罗溪之畔,也叫罗溪书院。“罗阁书声”是古琅岐十景之一。古代不大的琅岐岛,不仅有罗溪书院,还有其他的书院。如白云山上始建于明代的白云庵,当年就有奎光阁、朱子祠等建筑,也是岛上文士禊集之所。据记载,元代诗人董渭就世居在白云山下,学富五车却隐居不仕,曾邀“闽中十才子”林鸿、陈亮、高棅等游白云寺吟诗作赋。明代状元翁正春少时也寓居白云庵读书。他在《白云庵记》中盛赞白云山“胜可步武夷,丽可当三山”。今天,我们在寺院后面,还能看到刻着“朱子祠”的残碑和清嘉庆壬申(1812年)《公捐祀典》碑及道光《协建祠阁》的石碑。可惜,白云庵后来成了白云寺,近年来,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香火也越来越旺,但曾经的朱子祠除了残碑之外,都已无迹可寻了。另外,在上岐村鳌山上也有一座书院,可惜当年遭到日本人轰炸而被毁,现在也无迹可寻了。
朱子过化之处,往往文风日炽、教育兴盛,这与他主张创建书院、传道授业的积极作为相关。对朱子而言,岳麓、白鹿洞、武夷、考亭这四大书院,与他的研学、著述、传授乃至生命息息相关。据统计,宋元时期光福建一地,书院就有63所,而到明清时期,则达到400多所,这些书院的诞生与发展,与朱子以及其理学的传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在福州地区有案可稽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龙津书院、龙峰书院外,还有鳌峰书院、紫阳讲堂、东野竹林书院、贤场书院、高峰书院、濂江书院、文公书院、吟翠书院、丹阳书院、梅溪书院等等。特别是福州鳌峰书院,从宋到清以至民国,不管是作为私家读书处还是作为官府办学地,几百年来,它与朱子以及弟子黄榦等理学传承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还走出了像林则徐、梁章钜、陈化成等这样杰出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朱子,有了书院,八闽大地才加速改变了“蛮夷”形象,使福建在南宋、元、明、清文化格局里,有了一席之地,使福建能在近代发出了独特而重要的声音。
琅岐岛从宋到清,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进士有29名。现在的琅岐户籍人口不过七八万,在古代,至多也只能按万把人计罢,如果是这样,那么,琅岐进士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了。这能说与朱子过化没有一点关系吗?
罗溪书院有一幅长联,是清代里人的作品,内容如下:
廿余里琅山,收来眼底。登高凭眺,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腾石鼓,西耸金牌,北拥沙坡,南联矶岛,骚人硕士昔吟胜迹诗篇。揽五虎九龙,衬将起鹤礁猿屿;更排鳌翔凤,早相衔象岭狮峦。莫辜负卤田芳稻,远溆长芦,麦陇青瓜,著畦秾李。
千百年往事,注到心头。把卷流连,叹碌碌星霜易迈。想唐辟海陬,宋稠庐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贵胄善宗几易缥缃世业。即使节台星,只剩有断碑残碣;尽黄堂鸟府,悉付诸蔓草荒烟。仅赢得竹浦耕歌,墩峰樵唱,荻江渔火,罗阁书声。
上联描写琅岐岛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下联讲琅岐岛历史,人文荟萃,田园风光。特别是“唐辟海陬,宋稠庐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对海岛的历史人文做了形象而全面的表述,且隐含着海岛在宋代之后文风日盛、人才辈出,堪比海滨邹鲁这样的信息。
在明代,琅岐岛又称嘉登岛,辖七册十三墩,分别是:上琅琦(衙前、上岐)、下琅琦(下岐)、吴庄、洋下、海屿、后龙(云龙)、赤沙(金沙)、龙台、凤窝、凤翥(后水)以及今属于连江县的壶江、川石。围绕着罗溪书院的下琅琦(下岐)、吴庄、洋下、龙台、凤窝、凤翥(后水)等六个墩,就出了21名进士,这能说与靠近书院没有一点关系吗?朱子祠所在地竹浦、罗溪,均属于下琅琦(下岐),而下岐在古代就出了6名进士,数量居各墩之首,这难道也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琅岐岛,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表现存在,就是四处可见的祠堂。有专家说,岛上的这些明清宗祠建筑群,除了承载有福州历史乡愁外,还有着更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首先,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要地的重要见证。在岛上的龙台村刘氏宗祠里,人们可以从《唐司马参军刘贻孙世家族谱》中找到刘氏开港的历史记载,至于后来其他姓氏在岛上的开垦印记,也都可在保存于各大宗祠的族谱内找到印证。其次,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明清时期同类建筑研究的重要范本。琅岐现存的明清宗祠建筑群,虽多有重修,但一直保持建筑原貌。这些建筑,均为硬山顶构造,大量运用穿斗抬梁结构,大多由大门、照壁、藻井、拜亭及正厅构成,根据进深不同带有数量不一的天井,另有牌匾、官阶牌等文物,神龛内供有大量牌位,呈现“万代如见”的恢宏格局。而位于下岐村的董氏祠堂,其规模和内涵都堪称居岛上众多祠堂之首。
带着对朱子祠、罗溪书院、下岐村和祠堂之间内在联系的追问,我走进了董氏祠堂。
祠堂位于下岐牛屿山西麓,背山临街,始建于明嘉靖初年(约1522)。20世纪末进行了重修。宗祠面宽14.5米,纵深43米,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此外还有附属建筑270平方米。祠堂四周围封火高墙,三落透后,古建筑技术精湛,特点突出,尤其是明代的木构建筑独具一格。整个堂构为穿斗抬梁式木构架,工艺精致,造型生动。除了建筑本身让人眼睛发亮外,更主要的是其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记忆。
宗祠上下有楹联27副,且多为古代宦官名人所撰。如明代英武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黄道周撰写的“衣冠清节传三世,词赋声名著两都”的柱联就格外引人注目,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正厅悬挂的十多块牌匾中,有明崇祯皇帝赐给进士董洋河的“帝座纶音”匾额以及自宋代以来下岐董家所出的进士、文魁匾额,加起来有十几个,像明永乐十六年进士贵州左布政使董和、万历举人韶州司马董廷钦、明崇祯二年进士董谦吉、崇祯十五年进士董养河、清乾隆进士广东四会知县董文驹等。
董文驹,字罗峰。清乾隆三十一年辛卯进士,授福宁(今霞浦)、台湾副教授,迁广东肇庆府四会县令。在当地建有善政,因此得到了老百姓的感念。据说,他小时候师从岛上一位郑先生,因聪明好学,深受先生喜欢,可惜家贫不得不辍学。郑先生感到非常可惜,就到他家探访,见到了文驹的母亲。他母亲说,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孩子要去拾柴火补贴家用。郑先生立即就对文驹母亲说,你家的柴火由我来提供,文驹的学费也可以减免。后来,郑先生便带着文驹到了一个富人家里授馆(即当家庭教师)。主人家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郑先生就主动做媒,要主人把女儿许配给文驹。主人嫌弃文驹家境贫穷,想拒绝。郑先生就对这家主人说,文驹这孩子聪明好学,日后必定能出仕做官,我敢担保,你的女儿一定会当上七品夫人的。主人相信了郑先生的话,便把女儿许配给了文驹。夫妻和睦相敬,董文驹也发愤读书,果然中了进士,做了知县,夫人自然也成了七品夫人。董文驹写得一手好文章、好书法,流传至今的描绘琅岐观日之作《白云观日》,就是出自董文驹之手。“白云古寺白云天,东望微茫水接天,红日扶桑翻浪出,雷轰赤水火轮悬。”真的是情景交融,气势如虹……
从董氏的祠堂里,可以清楚地读出朱子祠、罗溪书院带给下岐人的教育与文化的熏陶是多么的浓厚了。实际上,带给下岐村的文化遗存远不止于此。离董氏祠堂不远处,就是朱氏祠堂。下岐朱氏是唐宋一门双宰相朱敬则和朱倬的后裔。祠堂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也很有历史韵味,门面镌刻着《朱子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洋溢着理学之光。牛屿山山麓除了董氏、朱氏两个祠堂外,还有妈祖宫、大王宫、蟒天神王庙、白马王庙、流灵尊王庙、关帝庙、九天玄女庙等古建筑,村里至今也还保留着好几条老街道,这些都向世人展现着这个村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想,今天请下岐村的老百姓都来支持再现朱子祠、罗溪书院昨日的风采,应当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罢!
站在即将修缮完工的朱子祠前,我遥想着当年这里的模样:青山绿水,山花烂漫,源于九龙山的溪水,沿着祠边潺潺流过,与水声相唱和的是琅琅书声,与山花相媲美的是英俊才郎……这座位于竹浦的朱子祠不当属于下岐村,也不仅仅属于琅岐,它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琅岐岛风采》一书(杨东汉著)对这座祠有这样的描述:“朱子祠始建年间已无从查考。据吴庄林有贵先生说,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林家美,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创建朱子祠,为首总理。以祠为文人雅士燕集之所,以振琅岐之文风。”该书还介绍说,朱子祠“四面烽火山墙,面宽约14米,纵深40米,四扇三间,三落透后,土木结构。头进天井、回廊古朴,中进为三开间,中为厅,旁两厢房,为文人读书之处,后进天井回廊,逐级升高,为朱子殿堂,中央奉祀朱子塑像”。
与很多类似的文化古迹的命运相比,琅岐的这座位于九龙山南麓一个叫竹浦的地方的朱子祠,算是幸运的。它曾经作为书院供学子读书,后来成了生产队办公场所,之后很长时间成了无人问津的旧屋。前年春节,我找到了这个地方,因年久失修,祠的好几根梁柱已被蛀虫侵蚀,有的已经落地歪躺在一旁,墙体也是斑驳陆离的,墙帽上的野草在冬日寒风里萋萋摇摆,一副疲惫模样。万幸的是,主体建筑没有坍塌。再看看岛上重修的多处寺院,香火缭绕,人声鼎沸。我为儒学,为朱文公扼腕长叹,也为人们对历史人文的漠视感到莫名的悲凉。
我不由地想到了古田县杉洋镇。当地的蓝田书院始建于唐代,朱子曾在书院学习、讲学,也因斗争在此避难过,并撰有《东斋记》。其题的“蓝田书院”四个大字,八百多年后依然熠熠生辉。虽然书院不幸于1975年12月在一场大火中烧毁,但2012年,当地乡贤余博士出资三百多万元重修了蓝田书院,并雇请一名教师在书院里为乡人普及国学知识。今天,杉洋人自豪地在镇中心位置立石勒记:“杉洋——朱熹过化之乡”!
琅岐岛上的朱子祠,何时也能焕发风采?
一番上下急切呼吁之后,省区市三级文物部门终于决定,对琅岐朱子祠进行修缮,并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保障。文物专家还叮嘱,祠有明代时期建筑的特点,应当认真保护修复。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近年来党和政府强调文化自信,强调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加大对文物保护的力度,已经有了一定实质性的效果。当我对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在表示祝贺之时也露出了惊讶的眼神,一座不大的海岛,还会有这等规模的朱子祠?为了回答朋友们的疑问,我开始关注起竹浦朱子祠的由来。
朱子祠,是祭祀朱子的场所。朱子,字晦翁,是孔孟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构建了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丰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宋至今,朱子理学不仅影响了中国八百多年,更成了东亚文化的核心内容。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二者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者堪与伦比。”著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这样判断:“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但朱子的一生不是都顺风顺水,到了晚年,还真可谓充满了坎坷。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朱子志同道合的好友赵汝愚被罢去宰相,朝政大权落入心怀野心的韩侘胄一帮手中。于是,凡是与韩侂胄意见不合的,都被称为“道学之人”。不久,道学又被斥责为“伪学”,四书、六经也都成了禁书。再不久,宁宗赵扩又下了诏,订立了所谓的“伪学逆党籍”,史称“庆元党禁”,名列其间者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朱子被斥为“伪学魁首”,名列黑名单第五,所列罪状多达十项,甚至有人提出,要“斩朱熹以绝伪学”。这一年,朱子66岁,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朱子依然讲学不辍,著述不断,也有史料记载,如《福建通志》:“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而在《长乐县志》《古田县志》《霞浦县志》《闽清县志》中,则都有朱子在当地避难寓居的信息。
朱子在闽江口有活动的足迹?这样的历史文字信息让我兴奋。盛夏里的一天,我与朋友一起来到了据说与朱子有着渊源的德成岩。德成岩坐落在今长乐市潭头镇西侧素有“洞天幽绝”之称的筹峰山中。它是福建历史上首位思想家唐代林慎思与其兄进思、景思等筑“月楼精舍”读书的地方。据长乐志记载,宋庆元元年(1195年),朱子避伪学之难寓居长乐时,曾来此凭吊,非常感佩林慎思的“儒英忠义”与“续孟功业”,谓其“德成于此”,于是将“月楼精舍”改为了“德成精舍”。朱子手迹“德成精舍”四个大字至今还镌刻在岩壁上,而岩壁下的泉水,也依然活泼、清冽无比。
21世纪初,为了展示这一文化骄傲,长乐市聚民力进行重修。因缺乏必要的引导与监督,老百姓在德成岩前新修建了一座阁楼,计划作为寺院。后经交涉,同意改为林慎思纪念馆,因为没有经济效益,民间也就缺乏了积极性,阁楼成了半拉子工程。站在现场,大家淌着汗水感慨不已。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长乐潭头镇二刘村的龙峰山上,寻找朱子当年在这里的“讲学处”。当年,村人刘砥、刘砺两兄弟跟从朱子在山上学习,后来,兄弟俩都中了进士。为感念朱子,便将这个地方改名为“晦翁岩”了。到了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率船队驻泊长乐太平港,曾在山上修建了一座龙峰书院。书院掩映在奇岩古树之间,环境清幽,空气清新,有“小洞天”之誉,也是福州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
走进山门,几块岩石耸立,构成了一处天然的幽荫之所。洞外千姿百态的太极榕、盘岩榕、红榕、油杉、罗汉松、红枫等树木遮云蔽日,洞内凉风习习,石凳、石桌、白鹿石雕、酷似两支如椽大笔贴着岩壁耸立而上的树干以及明代郑世威勒刻的“读书处”三个大字,无一不在努力还原着当年朱子与二刘在这里教学相长的情景。山外风雨正紧,洞内书声如故。就是在“禁伪学、除逆党”这样四处腥风的日子里,朱子依然为了理学而忙碌着,看得出,他的心里是如何的坦然与磊落!
我想起曾拜访过的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书院坐落在庐山的南麓山涧中,幽深、古朴。书院始建于唐朝,朱子知南康军(今九江星子县)时,力主重修了书院,并且为书院立下了学规。现在大家熟悉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朱子当年在白鹿洞书院立下的。白鹿洞书院里还真有一个白鹿洞,洞里也有一头白鹿石雕,栩栩如生。
龙峰书院原来是祀朱子和刘砥、刘砺的,后改称三贤祠。三贤祠在21世纪初也经过整修,基本上保持了明代风格。可惜,祠修复后,只是简单地委托给了同在一个山头的寺院管理。同行的二刘村人介绍说,寺院香火旺盛,面积越来越大,而三贤祠却因缺少资金、缺少关注,许多梁柱已经出现了白蚁,如不抓紧处理,三贤祠的倒塌只是个时间问题。我随手敲了敲,很多梁柱确实发出了“噗噗”的中空声。
龙峰书院对面的马尾亭江镇长安村和长柄村,也都有朱子的遗迹。于是,大家离开了晦翁岩,驱车上了琅岐大桥,经过琅岐岛,再开上闽江琅岐大桥,下了桥,不远处就是长安村。我们来到了一个叫西岩寺的地方。
寺院不很规则,但面积不小。最让人称奇的是,一个大堂里摆满了各路神仙菩萨。当地人说,这就是儒道佛的“和平共处”,也算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当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带路人领着我们穿过几个走廊,到了后院一处石壁前。石壁上刻着“仙苑”两个大字,楷书,每字高0.59米、宽0.53米左右,边上草署“晦翁书”,每字径约5.2厘米。
环顾四周,满目都是俗物,一点都体会不到身居仙苑的感觉,更无法体验朱子当年写下这两字时的心情。长安村就面临着闽江,是闽江入海口的一个重要渡口所在。古时候,坐在这里,泡上一壶茶,捧起一卷书,可以观白帆点点,迎清风拂面,对朱子来说,这里不是仙苑又是什么?今天,村里盖起了新楼,江水自然望不见了,“仙苑”两个大字也只能成了人们想象过去的引子。
隔着长安村的,叫长柄村,村里藏着一座福州地区目前规制最大的朱子祠。长柄朱子祠又名龙津书院,由门楼、大殿、文昌阁、后天井等组成,两边置风火墙,占地面积五百多平方米。朱子当年曾在此讲过学,当地人梁汝昌、郑庸斋等从之游,最后也都有了不小的成就。朱子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亭江举人董应举、郭复之等建造的,用来祭祀朱子及弟子梁汝昌、郑庸斋的。今天,祠内还保存着朱子题刻的“跃龙津”三字,门墙内壁嵌有明代董应举《建紫阳先生祠题词》、清代王有树《龙津书院祀典记》等碑刻。朱子祠刚刚经过修复,还散发着油漆香,让人心生快意。
我回望刚才经过的琅岐岛,岛上为什么会有朱子祠的答案似乎也一下子找到了。潭头的二刘村、亭江的长安村、长柄村,它们分别位于闽江的南岸和北岸,大约在一条直线上。不要说是水路舟楫古代,就是在今天,朱子要想过往这两个分别位于闽江南北岸的村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经过琅岐岛。于是,一个大胆的推理跳上心头,朱子曾经到过琅岐岛!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发现而击掌。
当时朱子是和什么人一起经过的?经过时有人知晓吗?为什么地方史志上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也许,南宋时,琅岐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岛,朱子避伪学之祸,出行也不可能大张旗鼓。虽然是悄悄地,但还是有人记住了,于是,才有了之后小岛的文明与开化?
我在更多的史料里读到了这样的信息。这座竹浦朱子祠,实际上也是一座书院,因为坐落在罗溪之畔,也叫罗溪书院。“罗阁书声”是古琅岐十景之一。古代不大的琅岐岛,不仅有罗溪书院,还有其他的书院。如白云山上始建于明代的白云庵,当年就有奎光阁、朱子祠等建筑,也是岛上文士禊集之所。据记载,元代诗人董渭就世居在白云山下,学富五车却隐居不仕,曾邀“闽中十才子”林鸿、陈亮、高棅等游白云寺吟诗作赋。明代状元翁正春少时也寓居白云庵读书。他在《白云庵记》中盛赞白云山“胜可步武夷,丽可当三山”。今天,我们在寺院后面,还能看到刻着“朱子祠”的残碑和清嘉庆壬申(1812年)《公捐祀典》碑及道光《协建祠阁》的石碑。可惜,白云庵后来成了白云寺,近年来,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香火也越来越旺,但曾经的朱子祠除了残碑之外,都已无迹可寻了。另外,在上岐村鳌山上也有一座书院,可惜当年遭到日本人轰炸而被毁,现在也无迹可寻了。
朱子过化之处,往往文风日炽、教育兴盛,这与他主张创建书院、传道授业的积极作为相关。对朱子而言,岳麓、白鹿洞、武夷、考亭这四大书院,与他的研学、著述、传授乃至生命息息相关。据统计,宋元时期光福建一地,书院就有63所,而到明清时期,则达到400多所,这些书院的诞生与发展,与朱子以及其理学的传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在福州地区有案可稽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龙津书院、龙峰书院外,还有鳌峰书院、紫阳讲堂、东野竹林书院、贤场书院、高峰书院、濂江书院、文公书院、吟翠书院、丹阳书院、梅溪书院等等。特别是福州鳌峰书院,从宋到清以至民国,不管是作为私家读书处还是作为官府办学地,几百年来,它与朱子以及弟子黄榦等理学传承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还走出了像林则徐、梁章钜、陈化成等这样杰出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朱子,有了书院,八闽大地才加速改变了“蛮夷”形象,使福建在南宋、元、明、清文化格局里,有了一席之地,使福建能在近代发出了独特而重要的声音。
琅岐岛从宋到清,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进士有29名。现在的琅岐户籍人口不过七八万,在古代,至多也只能按万把人计罢,如果是这样,那么,琅岐进士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了。这能说与朱子过化没有一点关系吗?
罗溪书院有一幅长联,是清代里人的作品,内容如下:
廿余里琅山,收来眼底。登高凭眺,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腾石鼓,西耸金牌,北拥沙坡,南联矶岛,骚人硕士昔吟胜迹诗篇。揽五虎九龙,衬将起鹤礁猿屿;更排鳌翔凤,早相衔象岭狮峦。莫辜负卤田芳稻,远溆长芦,麦陇青瓜,著畦秾李。
千百年往事,注到心头。把卷流连,叹碌碌星霜易迈。想唐辟海陬,宋稠庐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贵胄善宗几易缥缃世业。即使节台星,只剩有断碑残碣;尽黄堂鸟府,悉付诸蔓草荒烟。仅赢得竹浦耕歌,墩峰樵唱,荻江渔火,罗阁书声。
上联描写琅岐岛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下联讲琅岐岛历史,人文荟萃,田园风光。特别是“唐辟海陬,宋稠庐宇,明标宦绩,清振科名”,对海岛的历史人文做了形象而全面的表述,且隐含着海岛在宋代之后文风日盛、人才辈出,堪比海滨邹鲁这样的信息。
在明代,琅岐岛又称嘉登岛,辖七册十三墩,分别是:上琅琦(衙前、上岐)、下琅琦(下岐)、吴庄、洋下、海屿、后龙(云龙)、赤沙(金沙)、龙台、凤窝、凤翥(后水)以及今属于连江县的壶江、川石。围绕着罗溪书院的下琅琦(下岐)、吴庄、洋下、龙台、凤窝、凤翥(后水)等六个墩,就出了21名进士,这能说与靠近书院没有一点关系吗?朱子祠所在地竹浦、罗溪,均属于下琅琦(下岐),而下岐在古代就出了6名进士,数量居各墩之首,这难道也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琅岐岛,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表现存在,就是四处可见的祠堂。有专家说,岛上的这些明清宗祠建筑群,除了承载有福州历史乡愁外,还有着更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首先,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要地的重要见证。在岛上的龙台村刘氏宗祠里,人们可以从《唐司马参军刘贻孙世家族谱》中找到刘氏开港的历史记载,至于后来其他姓氏在岛上的开垦印记,也都可在保存于各大宗祠的族谱内找到印证。其次,琅岐的宗祠建筑群,是福州明清时期同类建筑研究的重要范本。琅岐现存的明清宗祠建筑群,虽多有重修,但一直保持建筑原貌。这些建筑,均为硬山顶构造,大量运用穿斗抬梁结构,大多由大门、照壁、藻井、拜亭及正厅构成,根据进深不同带有数量不一的天井,另有牌匾、官阶牌等文物,神龛内供有大量牌位,呈现“万代如见”的恢宏格局。而位于下岐村的董氏祠堂,其规模和内涵都堪称居岛上众多祠堂之首。
带着对朱子祠、罗溪书院、下岐村和祠堂之间内在联系的追问,我走进了董氏祠堂。
祠堂位于下岐牛屿山西麓,背山临街,始建于明嘉靖初年(约1522)。20世纪末进行了重修。宗祠面宽14.5米,纵深43米,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此外还有附属建筑270平方米。祠堂四周围封火高墙,三落透后,古建筑技术精湛,特点突出,尤其是明代的木构建筑独具一格。整个堂构为穿斗抬梁式木构架,工艺精致,造型生动。除了建筑本身让人眼睛发亮外,更主要的是其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记忆。
宗祠上下有楹联27副,且多为古代宦官名人所撰。如明代英武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黄道周撰写的“衣冠清节传三世,词赋声名著两都”的柱联就格外引人注目,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正厅悬挂的十多块牌匾中,有明崇祯皇帝赐给进士董洋河的“帝座纶音”匾额以及自宋代以来下岐董家所出的进士、文魁匾额,加起来有十几个,像明永乐十六年进士贵州左布政使董和、万历举人韶州司马董廷钦、明崇祯二年进士董谦吉、崇祯十五年进士董养河、清乾隆进士广东四会知县董文驹等。
董文驹,字罗峰。清乾隆三十一年辛卯进士,授福宁(今霞浦)、台湾副教授,迁广东肇庆府四会县令。在当地建有善政,因此得到了老百姓的感念。据说,他小时候师从岛上一位郑先生,因聪明好学,深受先生喜欢,可惜家贫不得不辍学。郑先生感到非常可惜,就到他家探访,见到了文驹的母亲。他母亲说,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孩子要去拾柴火补贴家用。郑先生立即就对文驹母亲说,你家的柴火由我来提供,文驹的学费也可以减免。后来,郑先生便带着文驹到了一个富人家里授馆(即当家庭教师)。主人家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郑先生就主动做媒,要主人把女儿许配给文驹。主人嫌弃文驹家境贫穷,想拒绝。郑先生就对这家主人说,文驹这孩子聪明好学,日后必定能出仕做官,我敢担保,你的女儿一定会当上七品夫人的。主人相信了郑先生的话,便把女儿许配给了文驹。夫妻和睦相敬,董文驹也发愤读书,果然中了进士,做了知县,夫人自然也成了七品夫人。董文驹写得一手好文章、好书法,流传至今的描绘琅岐观日之作《白云观日》,就是出自董文驹之手。“白云古寺白云天,东望微茫水接天,红日扶桑翻浪出,雷轰赤水火轮悬。”真的是情景交融,气势如虹……
从董氏的祠堂里,可以清楚地读出朱子祠、罗溪书院带给下岐人的教育与文化的熏陶是多么的浓厚了。实际上,带给下岐村的文化遗存远不止于此。离董氏祠堂不远处,就是朱氏祠堂。下岐朱氏是唐宋一门双宰相朱敬则和朱倬的后裔。祠堂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也很有历史韵味,门面镌刻着《朱子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洋溢着理学之光。牛屿山山麓除了董氏、朱氏两个祠堂外,还有妈祖宫、大王宫、蟒天神王庙、白马王庙、流灵尊王庙、关帝庙、九天玄女庙等古建筑,村里至今也还保留着好几条老街道,这些都向世人展现着这个村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想,今天请下岐村的老百姓都来支持再现朱子祠、罗溪书院昨日的风采,应当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罢!
站在即将修缮完工的朱子祠前,我遥想着当年这里的模样:青山绿水,山花烂漫,源于九龙山的溪水,沿着祠边潺潺流过,与水声相唱和的是琅琅书声,与山花相媲美的是英俊才郎……这座位于竹浦的朱子祠不当属于下岐村,也不仅仅属于琅岐,它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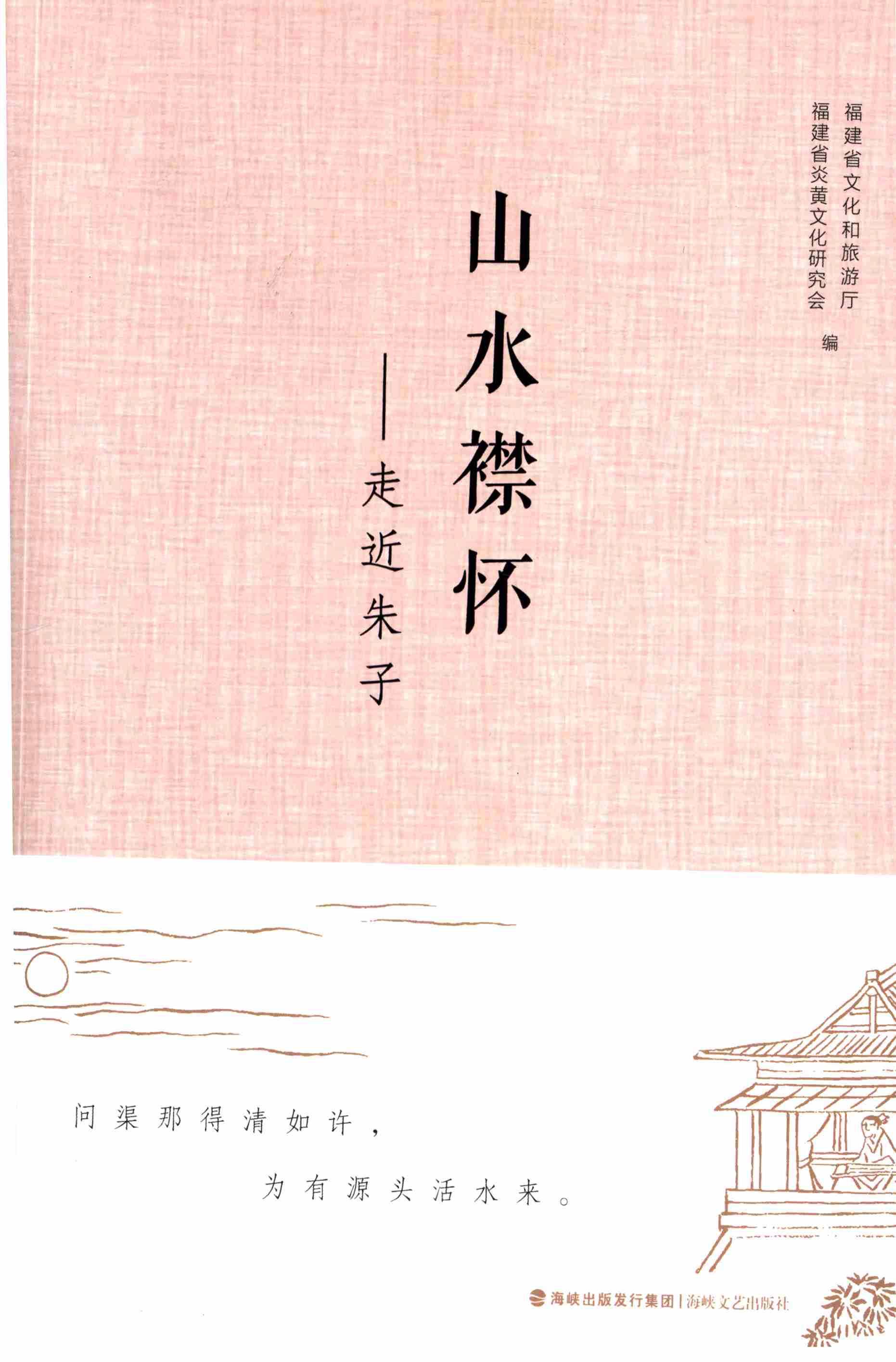
相关人物
何强
责任者
相关地名
福州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