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张栻对于《论语·学而篇》诠释之比较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904 |
| 颗粒名称: | 朱子与张栻对于《论语·学而篇》诠释之比较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12 |
| 页码: | 082-093 |
| 摘要: | 朱子和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他们都注释过《论语·学而篇》,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进行了解读。朱子注重建构《四书》体系,强调互相诠释,他的《论语集注》体现了他的思想特色。张栻则更加忠于原始的程朱理学,他的《论语解》较为保守。本文通过比较两人对《论语·学而篇》中的几个章节的注释,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异同。其中,“学而时习章”是重点讨论的章节,张栻和朱子都强调知行合一,但张栻更注重知、行的相互发明,而朱子认为行更为重要。两人的解释都源自程子的教诲。朱子的诠释更倾向于建构体系,引用了程子及其后学的观点,而张栻的解释更忠于程子的原意。总体而言,两人对于《论语·学而篇》的解释不尽相同,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性格和理学立场。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张栻 |
内容
一、前言
张栻(1133—1180)与朱子(1130—1200)都是南宋(1127—1279)著名理学家;朱子从学于李侗(李延平,1093—1163),属道南派,承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龟山,而龟山则为程子学生;而二程理学的另一脉,则为胡宏(1105—1161)的湖湘一系,张栻是胡宏学生,而胡宏的父亲胡安国,则是上承谢上蔡,上蔡亦为程子学生。
早年朱子欲学二程,先是就学于李侗,不久李侗去世,于是另觅管道,改投胡宏门下,却也无法如愿直接受业于胡宏,转而找到胡宏弟子张栻,并与张栻结为好友。①朱子与张栻皆属二程理学一脉,皆有《论语》注疏作品,《论语》一书对于二人之学术发展皆占有重要地位。朱子以《论语》作为《四书》之一来建构体系,著有《论语集注》;而张栻的《论语解》则为其个人代表作品。
张栻《论语解》作于乾道九年(1173),其中的相关注释亦曾与朱子做过讨论,而朱子的《论语集注》也会引用张栻的解说。②大致上,不管《论语解》或《论语集注》,内容皆以理学为中心旨趣,然毕竟二人各有不同体会。虽然张栻过世后,朱子尝对其遗著进行整理,可能删去一些不合己意的内容(推测应当不致进行增补)①,也因此拉近了两本著作的距离,但二人的学术性格仍有不同。
以朱子来说,虽以程子为本,但已朝建构之路迈进,个人思想特色较为鲜明,并且致力于《四书》思想之一贯,《四书》之间必须要能互相诠释,这是朱子的主要做法。而张栻虽然也有《孟子解》作品,但是并无建构体系之企图,较朱子合于原意,但也多少受到来自二程的理学制约。
本文将借由二人对于《论语·学而篇》的注说,来探讨《论语解》与《论语集注》彼此之异同,主要针对“学而时习章”、“其为人也孝弟章”、“弟子入则孝章”、“礼之用章”等四章。朱子为要疏通与建构《四书》之体系一致,对于“学而篇”此四章用心颇多,很能展现自家理气论与体用论之特色,本文即借此四章进行讨论。
二、“学而时习章”
(一)张栻的诠释
张栻对于“学而时习章”②诠释如下:
学贵于时习。程子曰“时复紬绎,浃洽于中也”,言学者之于义理,当时紬绎其端绪而涵泳之也。浃洽于中故说。说者,油然内慊也,有朋自远方来,则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资己,讲习相滋,其乐孰尚焉!乐比于说为发舒也。虽然,朋来固可乐,而人不知亦不愠也。盖为仁在己,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门人记此首章,不如是则非所以为君子也。③
“学贵于时习”——这是强调知、行并重的道理,本于程子“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学为知而习为行,知、行缺一不可。如张栻在《论语说序》也提到:
秦汉以来,学者失其传,其间虽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涂,莫适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穷理居敬之方开示学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尧舜之道。于是道学之传,复明于千载之下。然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①
学习上有两种违反中庸之道的弊病,一种是不知而行,如黑暗中探路,无所适从,另一种则是知而不行,终身未能躬行。这两种都违反了河南程氏“穷理居敬”的教诲,知与行务必并重才是!
此说近于朱子“知先行后”之说,而行更为重要,至于张栻则是主张知、行之间要相互发明。两人说法皆由程子“穷理居敬”一脉传下。
(二)朱子与张栻的比较
朱子诠释如下:
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纡问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②
朱子、张栻之同处,例如,张栻认为:“不如是则非所以为君子。”而朱子引其说,认为出于程子,程子言:“非乐不足以语君子。”又张栻比较悦与乐之不同,张栻认为:“乐比于说为发舒也。”而朱子引程子言:“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张栻言“发舒”,而朱子言“发散”,非常相近。
两人都提到程子的“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悦”,又张栻言:“而人不知亦不愠也。盖为仁在己,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而朱子引其出处,乃程颐弟子尹和靖之语:“而人不知亦不愠也。盖为仁在己,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尹氏之说可参见朱子所编《论孟精义》,尹氏言:“有朋自远方来,其道同而信之也,故乐,学在己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故曰君子。”③
可见,两人之诠释常是依于程子或程子后学而来。而朱子所编《论孟精义》,大致也是以理学门人如杨龟山、谢上蔡等人见解为主,较少选取何晏(195?—249?)以来的汉学诠释,因为朱子本欲建构理学而借此取代汉学。
至于二人之不同处(只是表面之不同,内容仍然相似),在于朱子以学是效、是觉,此乃张栻所未言。朱子在此提到:“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学者,效也,觉也,故后觉效先觉,则为学矣。再者,还要明善以复其初。
朱子于《大学》“明明德”处亦言“明善复其初”。“复其初”者,乃指人性中本有仁义礼智,所谓的“道义全具”,然今受染而不复其明,故要去污以复其本有性善之全体。朱子又尝于孟子“知皆扩而充之”处,注曰:“四端在我,随处发见。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①“本然之量”意指心性本来之满量;本来虽是满量,却因蒙蔽与放失其心而失去,今当复其本然,也就是回到性体的本然全部。
至于张栻则未明言“复其初”便指回到性善之全体,然细究之,也不是毫无此意。张栻尝言:
谓既知人皆有是四者,皆当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盖无穷也。充夫恻隐之端,而至于仁不可胜用;充夫羞恶之端,而至于义不可胜用;充夫辞让之端,而至于礼无所不备;充夫是非之端,而至于知无所不知。然皆其理之具于性者,而非外为之也。虽然,四端管乎万善,而仁则贯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仁之要也。②
首先,人性可扩充以至于无穷;再者,凡此皆为内在之事,不为外,即四端者,情也,而仁是性,性即理也。
朱子倡议当扩充以致回复本然之量,在此虽不易看出,但可从其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的解释来看,张栻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义礼知皆具于其性,而其所谓仁者,乃爱之理之所存也。唯其有是理,故其发见为不忍人之心。皆有是心,然为私欲所蔽,则不能推而达之,而失其性之所有者。③这便近于朱子的“复其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是本然之性体全具,不从外得,因着私欲所蔽,而失其性之整全。
可再比较朱子与张栻“浩然之气章”之解释。朱子释“浩然之气”,曰:“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亦是强调复于本来之浩然正气。而张栻则释:“……故贵于养之,养之而无害则浩然塞乎天地之间矣,其充塞也,非自外来,气体固若此也。”④气之体本有其充塞,而此充塞非自外来。
可见张栻之“学而时习章”中,虽未看到如朱子之“明善复其初”说,但性质上仍高度相似。①
三、“其为人也孝弟章”
(一)仁是体,孝弟是用
张栻解“其为人也孝弟章”如下:②
其为人也孝弟,与孟子所言“其为人也寡欲”、“其为人也多欲”立语同,盖言人之资质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顺慈良,自然鲜好犯上,不好犯上,况有悖理乱常之事乎?君子务本,言君子之进德每务其本,本立则道生而不穷。孝弟乃为仁之本,盖仁者无不爱也,而莫先于事亲从兄,人能于此尽其心,则夫仁民爱物皆由是而生焉。孝弟立则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举者也,或以为由孝弟可以至于仁,然则孝弟与仁为异体也,失其旨矣。③孝弟是“为仁”之本!至于“为仁”二字,究指“是仁”,抑或“行仁”,张栻并未明说,然反对“由孝弟可以至于仁”,因为“孝弟与仁为异体”,则张栻以仁为性、为体,是为形上,而孝弟是用,是为形下,两者不同体。这样的诠释和朱子相当接近。
(二)“为仁”乃指“行仁”,不指“是仁”
朱子与张栻的见解皆从程子而来。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何尝有孝弟?”性是理、是体,是形上,不为发用,而孝弟才是发用,是为形下,两者不同。又朱子尝言:“为仁”只能解为“行仁”,不可解为“是仁”。理由同样是“仁”已是体,最为根本,不能在体之上还有另个根本之体,所以孝弟只能是用,而“为仁”也不解为“是仁”,否则抵触程子理学,只能解为“行仁”,指的是实践“仁”要从孝弟开始,此途最为切近。
在此可举朱子之说以为比较。朱子言: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
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
“仁”为心之德、爱之理,这是理学的共识,张栻在《仁说》里亦如此形容“仁”。②仁是性理中四德之一,为形而上者,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是心中的德性,也是情爱之所以能爱的背后形上根据。朱子乃依程子之说,程子认为有两个“本”:若以“论性”(依据)而言,则仁为本,孝弟为用。而若以“行仁”(实践)而言,则孝弟是本,而后仁民;因为必先家齐而后国治,必先孝弟之亲亲,而后可以仁民爱物,仁民在孝弟之后。
那么,借由孝弟是否可以至“仁”?朱子引程子之说而予以否定,而张栻亦然。两人皆依程子而来,主张“仁”是性而孝弟是用,两者异体,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没有孝弟,孝弟只在用中,不在体中。
朱子所引程子之说,末后谈道:“仁主于爱。”仁者爱人,“仁”之性理发而为恻隐之心,此乃爱之情,故云“仁主于爱”。“仁”是爱之所以然之理,仁是形上,爱是形下。此说同于张栻。而爱者以爱亲为大,即以孝弟为重,故孝弟是行仁之根本。
在这一段,张栻与朱子的诠释字词虽不甚相同,但精神一致,颇有默契。③
四、“弟子入则孝章”
(一)朱子的诠释
《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④此章重点在于最后两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看似“先行,后知”。而朱子的体系建构是以《大学》为首,他将《大学》“格物”释为“穷理”,主张要先格物致知而后诚意,“诚意”乃是实践、“行”的层次。因此,依于朱子,乃是“先知,后行”!①
朱子主张“先知,后行”,而《论语》明言“先行,后知”,两者之间又该如何折合?朱子诠释如下:
以,用也。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②程子的解法重在主词“弟子”,而不是成人。若以朱子对于大学、小学的分序来看,小学阶段暂未格物穷理,格物穷理乃大学之事。如朱子的《大学章句·序》:“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③八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小学弟子,主要学习有二:(1)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2)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便符合朱子“弟子入则孝章”的诠释,必先行学洒扫、进退之礼,而后才来习学六艺之文。
然而,这里可以提出若干质疑。一者,六艺之中的射与御,并非是文;二者,《礼记·大学》一章之中,是否真有大学、小学之别?关于第二点,如日本江户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便曾提出异议,其言:“《集注》讥子游之不知有小学之叙,然游、夏同学于孔门,子夏独知有小学之叙,而子游不知之乎,观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诬也,盖子游疑其有所隐而讥之也。”④
此章原文为:“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乎!”⑤朱子认为子夏知道先小学后大学之序,而子张不知。然伊藤仁斋不表认同,因为两人既同学于孔子,怎会子夏知而子张不知?
话说回来,朱子以为,此章重点在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朱子主要是为学者立法,而不为圣人立法,因此强调必定要有《大学》“先知后行”之精神,这也恰与《论语》此章语势相违反。
其实,单从《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段,难以推出若不学文有何缺点。不过,朱子增补说,若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非但失之于野而已”。这些都是《论语》所无,也正好看出朱子的体系内涵,甚是重视学文、格物穷理。
朱子又或可举《论语》“子以四教章”来替自己辩解,其中,孔子提到四教:“文、行、忠、信”,朱子注曰:“其初须是讲学。讲学既明,而后修于行。所行虽善,然更须反之于心,无一毫不实处,乃是忠信。”①朱子借此,以为孔子亦言“先知后行”。不过,“子以四教章”是否果如朱子之解?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二)张栻的诠释
而张栻的诠释:
入孝出弟,谨行信言,泛爱亲仁,皆在己切要之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谓俟行此数事有余力而学文也,言当以是数者为本,余力学文也。若先以学文为心,则非笃实为己者矣,文谓文艺之事,圣人之言贯彻上下,此章虽言为弟为子之职,始学者之事,然充而极之,为圣为贤,盖不外是也。此数言先之以孝弟,盖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为本,推而达之也。②
张栻把弟与子分开,弟所职者为敬长,子所职者为尽孝,使合于原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甚者,敬长与尽孝亦不限于弟、子,而应当是学者终身之事。
那么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否意味当力行之事过多而无有余裕之际,也就不需学文了呢?张栻认为,这句话不应如字面上解,它只是强调学者当以力行为本,学文亦不当废弃,只是必定要能落实、实践。所谓文与实相对,实者,指力行忠信,文者,文艺,两者兼顾而成就一文质彬彬的君子,其中,当以力行为本,而学文接续。此张栻的意思。
张栻的诠解介于《论语》与朱子之间,并且似乎在替朱子“先知后行”、强调学文的说法解套。张栻与朱子都尝试响应“若行而无余裕,是否仍需学文”的问题,若回到《论语》,似乎是指“若无余裕,则不学文”,强调孝悌之事便是学人之根本,这点做不好,遑论其他。而朱子与张栻则都强调学文的重要性,朱子较为极端,张栻显得温和。
从这章来看,张栻较依《论语》做释,而朱子则依于自家《大学》“先知后行”的架构。
五、“礼之用章”
(一)朱子之诠释
《论语》原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朱子诠释如下: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①
此章诠释具有几个特点。首先,将“礼”解为“天理之节文”。然在《孟子》谈到“礼”的脉络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②“礼”乃是对于事亲从兄二事的节文,礼者,意指品节限制恰到好处!而朱子依于理学体系,则以“天理之节文”来定义“礼”,朱子比孟子多出“天理”二字。
至于“和”字,朱子释为“从容不迫”,这与前贤也有不同,而有两点可以讨论:
(1)前人常以“乐”释“和”,③而朱子也有这种意思,如引程子“礼胜则离,……乐胜则流”,又引范氏“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两者都把“和”与“乐”做出联系,这也是汉代学者较多采用的说法。
(2)朱子宗于理学,将“礼”视为体而非用。依于程子,性中只有仁义礼智,“礼”为四者之一,归属于体、天理,而为形上。学人所表现出的恭敬态度便是出于“礼”体,“礼”是恭敬之情的所以然之理,具有“严束”的意涵,所以,在另一方面,也就需要对于发用之处来加以调整、中和,使其“从容不迫”,而使“礼”能做到恰到好处!
不过,朱子的解法受到王船山(1619—1692)的质疑。船山言:
《集注》以从容不迫释“和”之义,则是谓人之用礼,必须自然娴适而后为贵。使然,将困勉以下者终无当于礼,而天下之不能繇礼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著为礼而已,未尝有所谓和也。从容不迫者,行礼者之自为之也。必从容不迫而后可为贵,则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后美矣。①朱子把“礼”视为体,而辞让、恭敬等视为用、视为情,提出“性发为情”,这是一种体系的建构。而船山之学属于气论,以张子为宗,提出“两端一致”、“性日生日成”等说,在解释上,自然不易认同朱子的理气论解法。
船山以为,关于“礼之用,和为贵”一句,是在讲述先王当初治理天下时所秉持的用意或原则,其中的“用”字,指行于天下,“和”字,指和顺人心,意指先王以制礼作乐来治理天下时,目的是能够和顺于人心要求,使推行于天下而无有烦难、阻碍。②
因此船山质疑,若把“和”字释为“从容不迫”,则主词是用礼之人而不是制礼之先王。用礼之人若属困勉无知,而不娴熟于礼,则礼终不贵、不美,待其人习得从容不迫而后可贵、可美。如此,就与原文之先王制礼作乐用以治理天下的初衷相差太多。
朱子的诠释虽与船山有些距离,却也同时凸显自家的体系样貌。朱子认为,“礼者,理也”,礼之全体大用,应当是既有严束亦有舒泰,既要和亦要节。严者,礼之体,故于发用处糅以“从容不迫”以致舒泰、中和;又过于“和”,则易有流弊,故如原文,当补以礼节。“和”、“节”相辅,以便成就全体大用、中和之道。
(二)张栻之诠释
朱子的诠释倾向理学建构,而张栻的诠释则可说是介于汉学与理学之间。张栻言:
礼主乎敬,而其用则和,有敬而后有和,和者,乐之所生也,礼乐必相须而成,故礼以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此为美,小大由之,而无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贵,务于和而已矣,不能以礼节之,则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盖为礼而不和,与夫和而无节,皆为偏弊也,礼乐分而言之,则为体为用,相须而成,合而言之,则本一而已矣。③
张栻在此先是提出“礼、乐相须”,而后又采用了体用论。“礼、乐相须”之说,出于汉学家,④汉学的诠释则依于礼记的《乐记》而来,如言:“礼胜则离,乐胜则流。”①而《乐记》的诠释则近于荀子。②又朱子的思想是以《四书》为本,择取孟子精神而不取荀子。③然礼乐精神乃是孟、荀所共。
而中国较早使用体用论者,如王弼以无为体、以无为用④,到了佛教风行,亦被广泛使用。宋明理学受到佛、老影响,也有体、用之说,如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亦用,同行异情”、程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张载批评佛老乃“体用殊绝”等,已经开始使用体用观,到了朱子更加明显。
朱子于“礼之用章”与“其为人也孝弟章”两章,都采用了体用论进行诠释,而张栻亦然。
若以原文来看,全文并未谈到“乐”,然而因着《礼记·乐记》的脉络,后人遂加入“乐”而一并诠解,到了程子亦以礼、乐并言。而朱子在“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处,如此形容“乐”:“乐则生矣,谓和顺从容,无所勉强,事亲从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⑤可见朱子把“乐”与“和”(从容不迫)几乎等同视之。
至于张栻,则以礼为体,以乐为用;此可与朱子比配,兹举数例,以见二人学说之相近:(1)朱子尝于“知者乐水章”言:“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⑥则仁智为体,乐寿为效用。(2)朱子对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一处,释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⑦又引程子所言“礼乐相须”云云,可见其视“乐”为“和”之发用,具有已发之用的意味。(3)朱子对于《中庸》的中与和,亦释为体、用,中为体而和为用。
六、结语与反思
朱子的诠释有其特色,与《论语》原意已是不同。他先以《大学》为骨架,而后接《论语》,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诠释《学而篇》,以便接轨于朱子创建的新本《大学》。《学而篇》的这四章诠释,皆颇具朱子学特色,而与先秦原意有了距离。
包括朱子的“学以复其初”、以仁义为体而孝弟为用、不学文而行则有弊,或如以礼为天理之节文而为体,等等,凡此,孔子皆无相关说法。而是朱子承自二程而来的体系建构,有着理学的特色。
至于张栻的说法则常淹没于朱学之中,反而近似朱子诠释。若要说两人之不同,可举以下两点:(1)朱子强调“先知后行”,否则必有弊病,但张栻并不强调这样的弊病;(2)“礼之用章”的诠释,乃采汉、宋合并之说,①此同于朱子的理学特色,但更能照顾到原文。
而两人《论语·学而篇》的诠释,相似性颇高。原因如前所述,包括两人皆是承自二程一脉而来、两人书信往来频繁而已有过沟通、朱子编辑张栻遗著而有所删编,等等。
大致上,朱子的诠释颇有特色,致使后来能在时代思潮中开出新局,成就一大家言之地位。而张栻则多近似朱子之说,自家特色较不明显。也许可以推测,纵使朱子不整理张栻遗著,两人思想仍是相当接近。
张栻(1133—1180)与朱子(1130—1200)都是南宋(1127—1279)著名理学家;朱子从学于李侗(李延平,1093—1163),属道南派,承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龟山,而龟山则为程子学生;而二程理学的另一脉,则为胡宏(1105—1161)的湖湘一系,张栻是胡宏学生,而胡宏的父亲胡安国,则是上承谢上蔡,上蔡亦为程子学生。
早年朱子欲学二程,先是就学于李侗,不久李侗去世,于是另觅管道,改投胡宏门下,却也无法如愿直接受业于胡宏,转而找到胡宏弟子张栻,并与张栻结为好友。①朱子与张栻皆属二程理学一脉,皆有《论语》注疏作品,《论语》一书对于二人之学术发展皆占有重要地位。朱子以《论语》作为《四书》之一来建构体系,著有《论语集注》;而张栻的《论语解》则为其个人代表作品。
张栻《论语解》作于乾道九年(1173),其中的相关注释亦曾与朱子做过讨论,而朱子的《论语集注》也会引用张栻的解说。②大致上,不管《论语解》或《论语集注》,内容皆以理学为中心旨趣,然毕竟二人各有不同体会。虽然张栻过世后,朱子尝对其遗著进行整理,可能删去一些不合己意的内容(推测应当不致进行增补)①,也因此拉近了两本著作的距离,但二人的学术性格仍有不同。
以朱子来说,虽以程子为本,但已朝建构之路迈进,个人思想特色较为鲜明,并且致力于《四书》思想之一贯,《四书》之间必须要能互相诠释,这是朱子的主要做法。而张栻虽然也有《孟子解》作品,但是并无建构体系之企图,较朱子合于原意,但也多少受到来自二程的理学制约。
本文将借由二人对于《论语·学而篇》的注说,来探讨《论语解》与《论语集注》彼此之异同,主要针对“学而时习章”、“其为人也孝弟章”、“弟子入则孝章”、“礼之用章”等四章。朱子为要疏通与建构《四书》之体系一致,对于“学而篇”此四章用心颇多,很能展现自家理气论与体用论之特色,本文即借此四章进行讨论。
二、“学而时习章”
(一)张栻的诠释
张栻对于“学而时习章”②诠释如下:
学贵于时习。程子曰“时复紬绎,浃洽于中也”,言学者之于义理,当时紬绎其端绪而涵泳之也。浃洽于中故说。说者,油然内慊也,有朋自远方来,则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资己,讲习相滋,其乐孰尚焉!乐比于说为发舒也。虽然,朋来固可乐,而人不知亦不愠也。盖为仁在己,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门人记此首章,不如是则非所以为君子也。③
“学贵于时习”——这是强调知、行并重的道理,本于程子“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学为知而习为行,知、行缺一不可。如张栻在《论语说序》也提到:
秦汉以来,学者失其传,其间虽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涂,莫适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穷理居敬之方开示学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尧舜之道。于是道学之传,复明于千载之下。然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①
学习上有两种违反中庸之道的弊病,一种是不知而行,如黑暗中探路,无所适从,另一种则是知而不行,终身未能躬行。这两种都违反了河南程氏“穷理居敬”的教诲,知与行务必并重才是!
此说近于朱子“知先行后”之说,而行更为重要,至于张栻则是主张知、行之间要相互发明。两人说法皆由程子“穷理居敬”一脉传下。
(二)朱子与张栻的比较
朱子诠释如下:
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纡问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②
朱子、张栻之同处,例如,张栻认为:“不如是则非所以为君子。”而朱子引其说,认为出于程子,程子言:“非乐不足以语君子。”又张栻比较悦与乐之不同,张栻认为:“乐比于说为发舒也。”而朱子引程子言:“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张栻言“发舒”,而朱子言“发散”,非常相近。
两人都提到程子的“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悦”,又张栻言:“而人不知亦不愠也。盖为仁在己,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而朱子引其出处,乃程颐弟子尹和靖之语:“而人不知亦不愠也。盖为仁在己,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尹氏之说可参见朱子所编《论孟精义》,尹氏言:“有朋自远方来,其道同而信之也,故乐,学在己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故曰君子。”③
可见,两人之诠释常是依于程子或程子后学而来。而朱子所编《论孟精义》,大致也是以理学门人如杨龟山、谢上蔡等人见解为主,较少选取何晏(195?—249?)以来的汉学诠释,因为朱子本欲建构理学而借此取代汉学。
至于二人之不同处(只是表面之不同,内容仍然相似),在于朱子以学是效、是觉,此乃张栻所未言。朱子在此提到:“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学者,效也,觉也,故后觉效先觉,则为学矣。再者,还要明善以复其初。
朱子于《大学》“明明德”处亦言“明善复其初”。“复其初”者,乃指人性中本有仁义礼智,所谓的“道义全具”,然今受染而不复其明,故要去污以复其本有性善之全体。朱子又尝于孟子“知皆扩而充之”处,注曰:“四端在我,随处发见。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①“本然之量”意指心性本来之满量;本来虽是满量,却因蒙蔽与放失其心而失去,今当复其本然,也就是回到性体的本然全部。
至于张栻则未明言“复其初”便指回到性善之全体,然细究之,也不是毫无此意。张栻尝言:
谓既知人皆有是四者,皆当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盖无穷也。充夫恻隐之端,而至于仁不可胜用;充夫羞恶之端,而至于义不可胜用;充夫辞让之端,而至于礼无所不备;充夫是非之端,而至于知无所不知。然皆其理之具于性者,而非外为之也。虽然,四端管乎万善,而仁则贯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仁之要也。②
首先,人性可扩充以至于无穷;再者,凡此皆为内在之事,不为外,即四端者,情也,而仁是性,性即理也。
朱子倡议当扩充以致回复本然之量,在此虽不易看出,但可从其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的解释来看,张栻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义礼知皆具于其性,而其所谓仁者,乃爱之理之所存也。唯其有是理,故其发见为不忍人之心。皆有是心,然为私欲所蔽,则不能推而达之,而失其性之所有者。③这便近于朱子的“复其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是本然之性体全具,不从外得,因着私欲所蔽,而失其性之整全。
可再比较朱子与张栻“浩然之气章”之解释。朱子释“浩然之气”,曰:“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亦是强调复于本来之浩然正气。而张栻则释:“……故贵于养之,养之而无害则浩然塞乎天地之间矣,其充塞也,非自外来,气体固若此也。”④气之体本有其充塞,而此充塞非自外来。
可见张栻之“学而时习章”中,虽未看到如朱子之“明善复其初”说,但性质上仍高度相似。①
三、“其为人也孝弟章”
(一)仁是体,孝弟是用
张栻解“其为人也孝弟章”如下:②
其为人也孝弟,与孟子所言“其为人也寡欲”、“其为人也多欲”立语同,盖言人之资质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顺慈良,自然鲜好犯上,不好犯上,况有悖理乱常之事乎?君子务本,言君子之进德每务其本,本立则道生而不穷。孝弟乃为仁之本,盖仁者无不爱也,而莫先于事亲从兄,人能于此尽其心,则夫仁民爱物皆由是而生焉。孝弟立则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举者也,或以为由孝弟可以至于仁,然则孝弟与仁为异体也,失其旨矣。③孝弟是“为仁”之本!至于“为仁”二字,究指“是仁”,抑或“行仁”,张栻并未明说,然反对“由孝弟可以至于仁”,因为“孝弟与仁为异体”,则张栻以仁为性、为体,是为形上,而孝弟是用,是为形下,两者不同体。这样的诠释和朱子相当接近。
(二)“为仁”乃指“行仁”,不指“是仁”
朱子与张栻的见解皆从程子而来。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何尝有孝弟?”性是理、是体,是形上,不为发用,而孝弟才是发用,是为形下,两者不同。又朱子尝言:“为仁”只能解为“行仁”,不可解为“是仁”。理由同样是“仁”已是体,最为根本,不能在体之上还有另个根本之体,所以孝弟只能是用,而“为仁”也不解为“是仁”,否则抵触程子理学,只能解为“行仁”,指的是实践“仁”要从孝弟开始,此途最为切近。
在此可举朱子之说以为比较。朱子言: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
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
“仁”为心之德、爱之理,这是理学的共识,张栻在《仁说》里亦如此形容“仁”。②仁是性理中四德之一,为形而上者,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是心中的德性,也是情爱之所以能爱的背后形上根据。朱子乃依程子之说,程子认为有两个“本”:若以“论性”(依据)而言,则仁为本,孝弟为用。而若以“行仁”(实践)而言,则孝弟是本,而后仁民;因为必先家齐而后国治,必先孝弟之亲亲,而后可以仁民爱物,仁民在孝弟之后。
那么,借由孝弟是否可以至“仁”?朱子引程子之说而予以否定,而张栻亦然。两人皆依程子而来,主张“仁”是性而孝弟是用,两者异体,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没有孝弟,孝弟只在用中,不在体中。
朱子所引程子之说,末后谈道:“仁主于爱。”仁者爱人,“仁”之性理发而为恻隐之心,此乃爱之情,故云“仁主于爱”。“仁”是爱之所以然之理,仁是形上,爱是形下。此说同于张栻。而爱者以爱亲为大,即以孝弟为重,故孝弟是行仁之根本。
在这一段,张栻与朱子的诠释字词虽不甚相同,但精神一致,颇有默契。③
四、“弟子入则孝章”
(一)朱子的诠释
《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④此章重点在于最后两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看似“先行,后知”。而朱子的体系建构是以《大学》为首,他将《大学》“格物”释为“穷理”,主张要先格物致知而后诚意,“诚意”乃是实践、“行”的层次。因此,依于朱子,乃是“先知,后行”!①
朱子主张“先知,后行”,而《论语》明言“先行,后知”,两者之间又该如何折合?朱子诠释如下:
以,用也。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②程子的解法重在主词“弟子”,而不是成人。若以朱子对于大学、小学的分序来看,小学阶段暂未格物穷理,格物穷理乃大学之事。如朱子的《大学章句·序》:“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③八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小学弟子,主要学习有二:(1)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2)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便符合朱子“弟子入则孝章”的诠释,必先行学洒扫、进退之礼,而后才来习学六艺之文。
然而,这里可以提出若干质疑。一者,六艺之中的射与御,并非是文;二者,《礼记·大学》一章之中,是否真有大学、小学之别?关于第二点,如日本江户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便曾提出异议,其言:“《集注》讥子游之不知有小学之叙,然游、夏同学于孔门,子夏独知有小学之叙,而子游不知之乎,观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诬也,盖子游疑其有所隐而讥之也。”④
此章原文为:“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乎!”⑤朱子认为子夏知道先小学后大学之序,而子张不知。然伊藤仁斋不表认同,因为两人既同学于孔子,怎会子夏知而子张不知?
话说回来,朱子以为,此章重点在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朱子主要是为学者立法,而不为圣人立法,因此强调必定要有《大学》“先知后行”之精神,这也恰与《论语》此章语势相违反。
其实,单从《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段,难以推出若不学文有何缺点。不过,朱子增补说,若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非但失之于野而已”。这些都是《论语》所无,也正好看出朱子的体系内涵,甚是重视学文、格物穷理。
朱子又或可举《论语》“子以四教章”来替自己辩解,其中,孔子提到四教:“文、行、忠、信”,朱子注曰:“其初须是讲学。讲学既明,而后修于行。所行虽善,然更须反之于心,无一毫不实处,乃是忠信。”①朱子借此,以为孔子亦言“先知后行”。不过,“子以四教章”是否果如朱子之解?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二)张栻的诠释
而张栻的诠释:
入孝出弟,谨行信言,泛爱亲仁,皆在己切要之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谓俟行此数事有余力而学文也,言当以是数者为本,余力学文也。若先以学文为心,则非笃实为己者矣,文谓文艺之事,圣人之言贯彻上下,此章虽言为弟为子之职,始学者之事,然充而极之,为圣为贤,盖不外是也。此数言先之以孝弟,盖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为本,推而达之也。②
张栻把弟与子分开,弟所职者为敬长,子所职者为尽孝,使合于原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甚者,敬长与尽孝亦不限于弟、子,而应当是学者终身之事。
那么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否意味当力行之事过多而无有余裕之际,也就不需学文了呢?张栻认为,这句话不应如字面上解,它只是强调学者当以力行为本,学文亦不当废弃,只是必定要能落实、实践。所谓文与实相对,实者,指力行忠信,文者,文艺,两者兼顾而成就一文质彬彬的君子,其中,当以力行为本,而学文接续。此张栻的意思。
张栻的诠解介于《论语》与朱子之间,并且似乎在替朱子“先知后行”、强调学文的说法解套。张栻与朱子都尝试响应“若行而无余裕,是否仍需学文”的问题,若回到《论语》,似乎是指“若无余裕,则不学文”,强调孝悌之事便是学人之根本,这点做不好,遑论其他。而朱子与张栻则都强调学文的重要性,朱子较为极端,张栻显得温和。
从这章来看,张栻较依《论语》做释,而朱子则依于自家《大学》“先知后行”的架构。
五、“礼之用章”
(一)朱子之诠释
《论语》原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朱子诠释如下: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①
此章诠释具有几个特点。首先,将“礼”解为“天理之节文”。然在《孟子》谈到“礼”的脉络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②“礼”乃是对于事亲从兄二事的节文,礼者,意指品节限制恰到好处!而朱子依于理学体系,则以“天理之节文”来定义“礼”,朱子比孟子多出“天理”二字。
至于“和”字,朱子释为“从容不迫”,这与前贤也有不同,而有两点可以讨论:
(1)前人常以“乐”释“和”,③而朱子也有这种意思,如引程子“礼胜则离,……乐胜则流”,又引范氏“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两者都把“和”与“乐”做出联系,这也是汉代学者较多采用的说法。
(2)朱子宗于理学,将“礼”视为体而非用。依于程子,性中只有仁义礼智,“礼”为四者之一,归属于体、天理,而为形上。学人所表现出的恭敬态度便是出于“礼”体,“礼”是恭敬之情的所以然之理,具有“严束”的意涵,所以,在另一方面,也就需要对于发用之处来加以调整、中和,使其“从容不迫”,而使“礼”能做到恰到好处!
不过,朱子的解法受到王船山(1619—1692)的质疑。船山言:
《集注》以从容不迫释“和”之义,则是谓人之用礼,必须自然娴适而后为贵。使然,将困勉以下者终无当于礼,而天下之不能繇礼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著为礼而已,未尝有所谓和也。从容不迫者,行礼者之自为之也。必从容不迫而后可为贵,则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后美矣。①朱子把“礼”视为体,而辞让、恭敬等视为用、视为情,提出“性发为情”,这是一种体系的建构。而船山之学属于气论,以张子为宗,提出“两端一致”、“性日生日成”等说,在解释上,自然不易认同朱子的理气论解法。
船山以为,关于“礼之用,和为贵”一句,是在讲述先王当初治理天下时所秉持的用意或原则,其中的“用”字,指行于天下,“和”字,指和顺人心,意指先王以制礼作乐来治理天下时,目的是能够和顺于人心要求,使推行于天下而无有烦难、阻碍。②
因此船山质疑,若把“和”字释为“从容不迫”,则主词是用礼之人而不是制礼之先王。用礼之人若属困勉无知,而不娴熟于礼,则礼终不贵、不美,待其人习得从容不迫而后可贵、可美。如此,就与原文之先王制礼作乐用以治理天下的初衷相差太多。
朱子的诠释虽与船山有些距离,却也同时凸显自家的体系样貌。朱子认为,“礼者,理也”,礼之全体大用,应当是既有严束亦有舒泰,既要和亦要节。严者,礼之体,故于发用处糅以“从容不迫”以致舒泰、中和;又过于“和”,则易有流弊,故如原文,当补以礼节。“和”、“节”相辅,以便成就全体大用、中和之道。
(二)张栻之诠释
朱子的诠释倾向理学建构,而张栻的诠释则可说是介于汉学与理学之间。张栻言:
礼主乎敬,而其用则和,有敬而后有和,和者,乐之所生也,礼乐必相须而成,故礼以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此为美,小大由之,而无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贵,务于和而已矣,不能以礼节之,则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盖为礼而不和,与夫和而无节,皆为偏弊也,礼乐分而言之,则为体为用,相须而成,合而言之,则本一而已矣。③
张栻在此先是提出“礼、乐相须”,而后又采用了体用论。“礼、乐相须”之说,出于汉学家,④汉学的诠释则依于礼记的《乐记》而来,如言:“礼胜则离,乐胜则流。”①而《乐记》的诠释则近于荀子。②又朱子的思想是以《四书》为本,择取孟子精神而不取荀子。③然礼乐精神乃是孟、荀所共。
而中国较早使用体用论者,如王弼以无为体、以无为用④,到了佛教风行,亦被广泛使用。宋明理学受到佛、老影响,也有体、用之说,如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亦用,同行异情”、程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张载批评佛老乃“体用殊绝”等,已经开始使用体用观,到了朱子更加明显。
朱子于“礼之用章”与“其为人也孝弟章”两章,都采用了体用论进行诠释,而张栻亦然。
若以原文来看,全文并未谈到“乐”,然而因着《礼记·乐记》的脉络,后人遂加入“乐”而一并诠解,到了程子亦以礼、乐并言。而朱子在“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处,如此形容“乐”:“乐则生矣,谓和顺从容,无所勉强,事亲从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⑤可见朱子把“乐”与“和”(从容不迫)几乎等同视之。
至于张栻,则以礼为体,以乐为用;此可与朱子比配,兹举数例,以见二人学说之相近:(1)朱子尝于“知者乐水章”言:“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⑥则仁智为体,乐寿为效用。(2)朱子对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一处,释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⑦又引程子所言“礼乐相须”云云,可见其视“乐”为“和”之发用,具有已发之用的意味。(3)朱子对于《中庸》的中与和,亦释为体、用,中为体而和为用。
六、结语与反思
朱子的诠释有其特色,与《论语》原意已是不同。他先以《大学》为骨架,而后接《论语》,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诠释《学而篇》,以便接轨于朱子创建的新本《大学》。《学而篇》的这四章诠释,皆颇具朱子学特色,而与先秦原意有了距离。
包括朱子的“学以复其初”、以仁义为体而孝弟为用、不学文而行则有弊,或如以礼为天理之节文而为体,等等,凡此,孔子皆无相关说法。而是朱子承自二程而来的体系建构,有着理学的特色。
至于张栻的说法则常淹没于朱学之中,反而近似朱子诠释。若要说两人之不同,可举以下两点:(1)朱子强调“先知后行”,否则必有弊病,但张栻并不强调这样的弊病;(2)“礼之用章”的诠释,乃采汉、宋合并之说,①此同于朱子的理学特色,但更能照顾到原文。
而两人《论语·学而篇》的诠释,相似性颇高。原因如前所述,包括两人皆是承自二程一脉而来、两人书信往来频繁而已有过沟通、朱子编辑张栻遗著而有所删编,等等。
大致上,朱子的诠释颇有特色,致使后来能在时代思潮中开出新局,成就一大家言之地位。而张栻则多近似朱子之说,自家特色较不明显。也许可以推测,纵使朱子不整理张栻遗著,两人思想仍是相当接近。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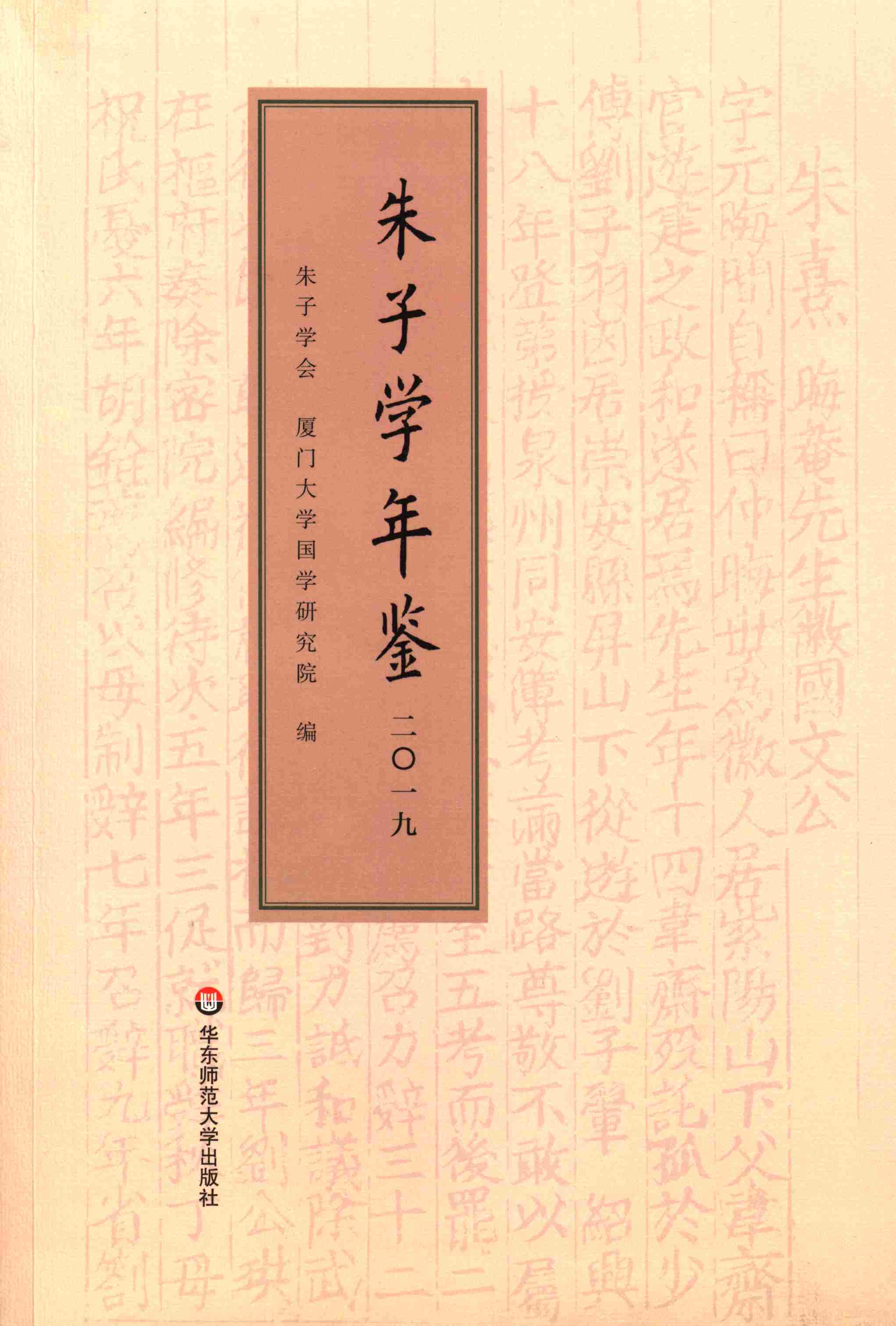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