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据《大学或问》说明朱子对“明德”的理解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901 |
| 颗粒名称: | 四、据《大学或问》说明朱子对“明德”的理解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5 |
| 页码: | 075-079 |
| 摘要: | 明德包含了心与理两者的关联,心是主体,理的意义在于心中得以彰显。人具有虚灵的心,而在心中万理咸备。因此,心具有本知理的作用,是人可贵之处。朱子认为人本来就有对道德之理的本知,在心中就能展现出来。朱子认为明德是人的本有,不管是何人,即使是昏愚之人,在情绪未发之时,都可以有明德的彰显。这表明明德的表现是可能的,也是人成德的根据所在。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明德说 |
内容
我认为上文对朱子之“明德说”的解释,应可以成立。在朱子的《大学或问》中,有些文字明白表示此意:
“然则此篇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①
据此段朱子所理解的明德,固然重理,但乃是兼理与气,即必须关联到心来说,此处心是主体,由于有心的主宰性的作用,理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他从人得五行之秀,故人有虚灵的心,而在心中万理咸备。固然之所以会以心为贵,是由于心能具理而彰显理,故明德之德,当然重在理,但由于人有灵明的心,故理在心中本来就可以得到彰显,于是这就是如上文所说的成德的超越根据,故致知之知是有对理的本知作为根据,致知就是从已知进至真知。人本来就有对道德之理的本知,这就是人比其他动物可贵的地方。而根据这一对性理的本知,人就可以做到如同圣人般参天地、赞化育。固然参赞是最后才能达到的境界,但成圣的根据,人人本有。据此可知朱子是从人人都有由五行之秀、正通之气构成的可以具众理的心来说人之可贵。如上引文所说“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故朱子所理解的人之所贵,在于人具有本知理的心。有此心,就有此理。他是关联到心知与理两者,即有此心就有性理来说人之可贵,并不是单说心或单说理为人所有来说人之可贵。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确定朱子所说的明德是心、理二者关联在一起,虽然是二者相关联,但必须是先验的及必然的关联在一起的。当然,由于心、理为二,故此本知理而与理关联在一起的心,并不是即是理的实体性的本心,而且心知理的程度,须用工夫来加强。需要对性理(道德之理)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真知,故后文续云:
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成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②
朱子此段反复说明德于人是本有的,一般人或下愚者因为气质的限制、私欲的蒙蔽,使本有的明德不容易彰显;但虽如此,明德还是有表现出来的可能,故曰“明德未尝息”,这就可以证朱子认为即使是下愚者,明德还是可以在其生命中表现出来。朱子所说的明德,虽然不等于陆王所说的心即理的本心,而是在心知中有性理的明白彰显,心与理虽然为二,但这种明德的彰显,虽在下愚也是可能的。此即表达了上文所说的明德作为成德的超越根据之意,也可以证朱子的成德理论或工夫论,是如同程伊川所说的人本有常知,可以根据此常知进到真知的地步。虽然程朱都强调后天的格物致知工夫,但此工夫是有先天本有的对于德性的本知作为根据的。上引文朱子认为不管是何人,即使是昏昧之极者,即下愚之人,在其情绪未发之时,都可以有明德洞然,即明德彰显之时,虽然其彰显可能是非常短的时间。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凡是人都可以有明德彰显之时,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所在。当然这个成德的可能或超越根据,并不能如陆王或孟子所说的本心良知,只要把此心体扩充,充分实现出来就可以,而必须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格物穷理,虽然如此,格物穷理的工夫是有“本体之明”作为根本,并非是全靠后天的认识才能明理。朱子续云:
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此段说明了不论是在大学或是在小学,都是根据本有的明德之明而作教学的工夫。可以说在小学是通过洒扫应对的生活教育来培养明德(“养之于小学之中”的“之”是指明德),在大学则是通过格物致知来使明德进一步彰显,乃至于使心知充分明理,而恢复理的全体的意义,对于理的表里精粗都能了解,也就是心知的全体大用充分明朗。这虽然是从心知与理两方面说,但二者也是关联在一起,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朱子的小学与大学的教学工夫,都是有本有的明德作为根据,通过大学的格物致知的工夫,就可以恢复心的全体,这所谓全体,就是心知对于本知的性理得到完全的了解,这也就同于伊川从常知到真知的程序。而且即使到此地步,也是人人本有的明德之发挥,并非在性分之外,另作增加的、没有本源之事。朱子续云:
向也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①
这是通过自明其明德而新民,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本于原有的明德而自己用工夫,加以进一步彰显,虽然做到充分明明德的地步,也不是对于人人本有的明德有所增加,由此也可见,朱子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而使心知理达到充分明白的地步,只是恢复明德的本体之明,并不是有所增加,这表示心知对于理的充分明白,只是对本来有的做加强的工夫,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本来没有的认识。这一方面肯定对于理本来有所了解的明德人人都有,而且会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主张必须进一步求知,到对于理有真知,才能持久地维持道德的实践,这是朱子强调道问学之意,但不能因为强调道问学,就说朱子不肯定人对道德之理本有所知,以致其格物致知是求理于外的“义外”之论。从以上《大学或问》的说法,可证朱子并非如牟先生所说的,是“后天渐教”的义理型态,由于对明德本有,而且未尝作出肯定,则朱子这一渐教的系统有先天的根据。故朱子的格物致知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通过心知对理的真切了解而恢复本有的明德之全体大用,在人人本有的明德此一意义上说,人的心知本来具理,而性理本来也有其光明的作用。由于心性二而不二,可以这样相互补充地来说。
在《大学或问》论知的一段,很能表达“知”的特殊性: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欲勉强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②
此段说“知”是心之神明,此一说法,比“心者,人之神明”③更进了一步。心是人之神明,而知则是心之神明,表示了“知”是心的最本质的作用。此一表示可以了解明德注所说的“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固然是说心的作用,但可以更确定地说,这是知的妙用。知的作用是所谓“妙众理”,说“妙众理”是比“具众理”更进一步的,这是表达了“知”把理的意义、作用具体表现出来之意。在《大学纂疏》引的《语录》曰:“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第13页)以虚灵来规定心之本体,就表示了此虚灵是知,而知是心之神明之意。据此,此知并不能理解为心、理为二的心之认知作用,而是此知之虚灵,与性理是相关联的,也可以说知中有理,能充分发挥此知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虚灵不昧的作用),则知中的理,就可以彰显出来。由此可证,朱子所说致知,不止是致心之认知作用,而是知与理都在其中。又在“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处,引语录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第32页)此段很能说明上述之意。理是自己本有的,故知理并非知一外在对象,而是将在我之理发出来。如果不是知中含理,或如上文所说,知与理有先验的关联性,是不能如此说的。
以上论明德,认为当以心关联性理而言,而此关联有先验性;实践的客观根据是理,然而心知对于理本有所知,吾人以为这是朱子言明德之本意,但朱子的有关言论,确有使人从心说明德或从性说明德两种解读的可能,由此也可以理解何以朱子之后会有明德如何理解、如何规定的论争,朱子对明德的规定,确有模棱两可处。朝鲜朝的学者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认为朱子对于心的看法可以分为“以理言”与“以气言”,而以理言之心就是明德,明德注中所说的虚灵固然是心,但这是以理言之心,故明德须以理来规定,这是所谓“明德是理”之说。虽然他说明德是理,但其实是关联到心来说的理,也表示了理在心中有其作用,故可以说明德。他将朱子明德注中所涉及的心性情三者都说是理。他这一说法在他的弟子中,引发了争论。柳重教(号省斋,1821—1893)对师说作了修正,认为心的“正说”应该还是从气来规定。他的同门金平默(号重庵,1819—1891),与他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他们俩人的门人继续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是朝鲜朝儒学史上后期的一个重要论争。①当时另一名儒田愚(号艮斋,1841—1922)对华西“明德是理”之说大加反对,主张“明德是心”。艮斋对明德之规定,大体同于牟宗三先生之说。这场朝鲜朝之论争与本文所论,可以有对照之作用,但其中论辩颇多曲折,须另作专文来讨论。
“然则此篇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①
据此段朱子所理解的明德,固然重理,但乃是兼理与气,即必须关联到心来说,此处心是主体,由于有心的主宰性的作用,理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他从人得五行之秀,故人有虚灵的心,而在心中万理咸备。固然之所以会以心为贵,是由于心能具理而彰显理,故明德之德,当然重在理,但由于人有灵明的心,故理在心中本来就可以得到彰显,于是这就是如上文所说的成德的超越根据,故致知之知是有对理的本知作为根据,致知就是从已知进至真知。人本来就有对道德之理的本知,这就是人比其他动物可贵的地方。而根据这一对性理的本知,人就可以做到如同圣人般参天地、赞化育。固然参赞是最后才能达到的境界,但成圣的根据,人人本有。据此可知朱子是从人人都有由五行之秀、正通之气构成的可以具众理的心来说人之可贵。如上引文所说“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故朱子所理解的人之所贵,在于人具有本知理的心。有此心,就有此理。他是关联到心知与理两者,即有此心就有性理来说人之可贵,并不是单说心或单说理为人所有来说人之可贵。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确定朱子所说的明德是心、理二者关联在一起,虽然是二者相关联,但必须是先验的及必然的关联在一起的。当然,由于心、理为二,故此本知理而与理关联在一起的心,并不是即是理的实体性的本心,而且心知理的程度,须用工夫来加强。需要对性理(道德之理)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真知,故后文续云:
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成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②
朱子此段反复说明德于人是本有的,一般人或下愚者因为气质的限制、私欲的蒙蔽,使本有的明德不容易彰显;但虽如此,明德还是有表现出来的可能,故曰“明德未尝息”,这就可以证朱子认为即使是下愚者,明德还是可以在其生命中表现出来。朱子所说的明德,虽然不等于陆王所说的心即理的本心,而是在心知中有性理的明白彰显,心与理虽然为二,但这种明德的彰显,虽在下愚也是可能的。此即表达了上文所说的明德作为成德的超越根据之意,也可以证朱子的成德理论或工夫论,是如同程伊川所说的人本有常知,可以根据此常知进到真知的地步。虽然程朱都强调后天的格物致知工夫,但此工夫是有先天本有的对于德性的本知作为根据的。上引文朱子认为不管是何人,即使是昏昧之极者,即下愚之人,在其情绪未发之时,都可以有明德洞然,即明德彰显之时,虽然其彰显可能是非常短的时间。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凡是人都可以有明德彰显之时,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所在。当然这个成德的可能或超越根据,并不能如陆王或孟子所说的本心良知,只要把此心体扩充,充分实现出来就可以,而必须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格物穷理,虽然如此,格物穷理的工夫是有“本体之明”作为根本,并非是全靠后天的认识才能明理。朱子续云:
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此段说明了不论是在大学或是在小学,都是根据本有的明德之明而作教学的工夫。可以说在小学是通过洒扫应对的生活教育来培养明德(“养之于小学之中”的“之”是指明德),在大学则是通过格物致知来使明德进一步彰显,乃至于使心知充分明理,而恢复理的全体的意义,对于理的表里精粗都能了解,也就是心知的全体大用充分明朗。这虽然是从心知与理两方面说,但二者也是关联在一起,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朱子的小学与大学的教学工夫,都是有本有的明德作为根据,通过大学的格物致知的工夫,就可以恢复心的全体,这所谓全体,就是心知对于本知的性理得到完全的了解,这也就同于伊川从常知到真知的程序。而且即使到此地步,也是人人本有的明德之发挥,并非在性分之外,另作增加的、没有本源之事。朱子续云:
向也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①
这是通过自明其明德而新民,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本于原有的明德而自己用工夫,加以进一步彰显,虽然做到充分明明德的地步,也不是对于人人本有的明德有所增加,由此也可见,朱子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而使心知理达到充分明白的地步,只是恢复明德的本体之明,并不是有所增加,这表示心知对于理的充分明白,只是对本来有的做加强的工夫,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本来没有的认识。这一方面肯定对于理本来有所了解的明德人人都有,而且会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主张必须进一步求知,到对于理有真知,才能持久地维持道德的实践,这是朱子强调道问学之意,但不能因为强调道问学,就说朱子不肯定人对道德之理本有所知,以致其格物致知是求理于外的“义外”之论。从以上《大学或问》的说法,可证朱子并非如牟先生所说的,是“后天渐教”的义理型态,由于对明德本有,而且未尝作出肯定,则朱子这一渐教的系统有先天的根据。故朱子的格物致知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通过心知对理的真切了解而恢复本有的明德之全体大用,在人人本有的明德此一意义上说,人的心知本来具理,而性理本来也有其光明的作用。由于心性二而不二,可以这样相互补充地来说。
在《大学或问》论知的一段,很能表达“知”的特殊性: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欲勉强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②
此段说“知”是心之神明,此一说法,比“心者,人之神明”③更进了一步。心是人之神明,而知则是心之神明,表示了“知”是心的最本质的作用。此一表示可以了解明德注所说的“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固然是说心的作用,但可以更确定地说,这是知的妙用。知的作用是所谓“妙众理”,说“妙众理”是比“具众理”更进一步的,这是表达了“知”把理的意义、作用具体表现出来之意。在《大学纂疏》引的《语录》曰:“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第13页)以虚灵来规定心之本体,就表示了此虚灵是知,而知是心之神明之意。据此,此知并不能理解为心、理为二的心之认知作用,而是此知之虚灵,与性理是相关联的,也可以说知中有理,能充分发挥此知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虚灵不昧的作用),则知中的理,就可以彰显出来。由此可证,朱子所说致知,不止是致心之认知作用,而是知与理都在其中。又在“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处,引语录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第32页)此段很能说明上述之意。理是自己本有的,故知理并非知一外在对象,而是将在我之理发出来。如果不是知中含理,或如上文所说,知与理有先验的关联性,是不能如此说的。
以上论明德,认为当以心关联性理而言,而此关联有先验性;实践的客观根据是理,然而心知对于理本有所知,吾人以为这是朱子言明德之本意,但朱子的有关言论,确有使人从心说明德或从性说明德两种解读的可能,由此也可以理解何以朱子之后会有明德如何理解、如何规定的论争,朱子对明德的规定,确有模棱两可处。朝鲜朝的学者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认为朱子对于心的看法可以分为“以理言”与“以气言”,而以理言之心就是明德,明德注中所说的虚灵固然是心,但这是以理言之心,故明德须以理来规定,这是所谓“明德是理”之说。虽然他说明德是理,但其实是关联到心来说的理,也表示了理在心中有其作用,故可以说明德。他将朱子明德注中所涉及的心性情三者都说是理。他这一说法在他的弟子中,引发了争论。柳重教(号省斋,1821—1893)对师说作了修正,认为心的“正说”应该还是从气来规定。他的同门金平默(号重庵,1819—1891),与他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他们俩人的门人继续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是朝鲜朝儒学史上后期的一个重要论争。①当时另一名儒田愚(号艮斋,1841—1922)对华西“明德是理”之说大加反对,主张“明德是心”。艮斋对明德之规定,大体同于牟宗三先生之说。这场朝鲜朝之论争与本文所论,可以有对照之作用,但其中论辩颇多曲折,须另作专文来讨论。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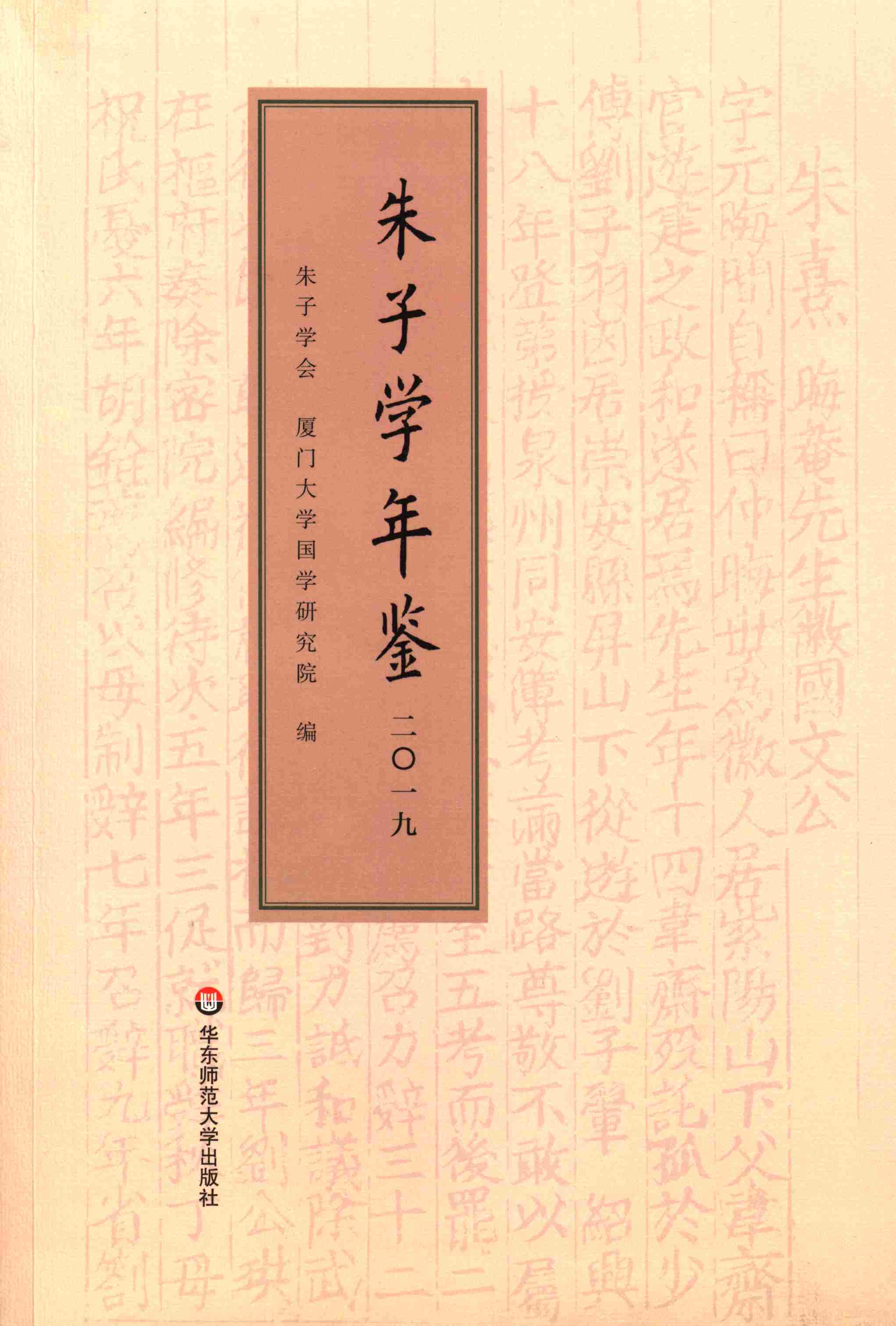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杨祖汉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