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牟先生对朱子“明德说”的诠释与朱子的原意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900 |
| 颗粒名称: | 三、论牟先生对朱子“明德说”的诠释与朱子的原意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6 |
| 页码: | 070-075 |
| 摘要: |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对明德的规定应以性理为主,将心性二者作明白的区分。他认为,在朱子的理论中,性是心的认知对象,心的活动是认识的作用,通过认识性理而为善。他指出,心并不是自发自律地给出道德行为的本心作用,而是依据性理为心所知的对象,进行实践的意志他律的行动。牟先生修改了朱子的“明德注”,将明德规定为人之所得于天的光明正大的性理,而虚灵不昧专属于心,是心知通过认知能力来管摄性理。这样理解明德,确实明确了心性二分,但弱化了心的知理是先验的,以及心统性情在明德中的关联性。牟先生的修改表达了朱子的心性二分思想,但在说明明德注时,削弱了心统性情的先验关联和心本来的妙用。虽然牟先生的修改清楚地表达了心性二分的观点,但可能忽略了明德注中心性相关联的含义。因此,牟先生的修改虽明确,但可能丢失了明德注本来包含的一些意思。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明德说 |
内容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对明德的规定虽然是性关联着心来说,但应该以性理为主,而且心性二者在朱子有截然的区分,性是心的认知对象,心知的活动是认识的作用,由认识性理而为善,心不是自发自律的给出道德行为的本心的作用,性理为心所知的对象,只是存有之理而没有活动性,于是这种心依理而行的实践,并非由性体不容已而自发给出来的实践活动,而为心通过认知的作用,关联到超越的性理,于是依理而行,性理为心所依的对象,故这种道德的实践,是意志的他律的型态。这是牟先生所理解的朱子的实践理论之型态,于是他认为朱子的“明德注”并未能明白表示此意,应该按照上说的朱子确定之意作修改,需要把心性二者作明白的区分,牟先生的说法如下:
是故依朱子之说统,其在《大学》中关于明德所作之注语实当修改如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可以由虚灵不昧之心知之明以认知地管摄之”之光明正大之性理之谓也。如此修改,不以“虚灵不昧”为首出之主词,省得摇转不定,而亦与朱子之思想一贯。若如原注语,则很易令人误会为承孟子而来之陆王之讲法。①
牟先生这样修改,就确定地把明德规定为“人所得于天的光明正大的性理”,即“明德”只就性理来说。而虚灵不昧专是就心而言,人的心知以其本有的,虚灵不昧的认知能力管摄性理。如此理解明德,则固然清楚区分心性为二,但亦突显心的知理是通过后天的认识而知之义,于是心的知理是没有保证的,人的心知可以知理也可以不知理。经过牟先生这样明确的规定,朱子论明德时,有些意思就似乎被淘汰掉了。如上文所说的,朱子在论明德时心与性是分不开的,“说一个,另一个随到”,依照朱子这些话,心与性在明德处是分不开的。如果二者是分不开的,则可以说是有先验的关联性。另外,明德的作用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此就表示了心统性情之义。心具众理是应万事的根据,故心管摄性理就能够应万事,能应万事是心统性的作用,而应万事的活动就表现了情,故朱子论明德包含了心统性情之义。以此为明德,则心统性情亦是心本有的性能,即心之虚灵本来便可具众理而表现四端来应万事,此心性情三者,在明德中本来是关联在一起的。或可说,由于这三者本来就相关联,于是总起来说明德。如果此说可通,则就不能说心要通过后天的经验认知,才可以关联性理,而表现为四端之情。若依牟先生对“明德注”之修改,心统性情是心之功能,并不能归诸明德。①即不能从明德说心统性情,心的统性情的作用,是通过心知的后天的作用。如此一来,便削弱了以此明德为人人本具的本体之明之义。即心之虚灵的作用是明德本具的,故曰:“心之体用本来如是”,此明是人人原则上有的、本具的妙用,如果这种作用充分发挥,就是心的“全体大用”,所谓心的全体大用,应该是就实现心本来的知理之明,表现心统性情的作用。如果是心通过后天的认知作用而关联到性理,则此妙用及明理之“本来如是”,即本然义,便去掉了。
故牟先生对“明德注”的修改固然很清楚地表达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朱子见解,但以此来解释明德注,则心须通过后天经验的认知作用,才能知理,依理而行,此是后天之渐教,心知理及依理而行,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心之知理是须通过格物穷理以知之,从存在之然之曲折处明善,即从善之事物处明其所以然,这是从“然”以知其“所以然”,这亦不能保证能知道德之理。但牟先生此释于朱子文意,似不甚顺适。因为明德注的原文相当清楚地表示明德是人所得于天,是人人本来便有,而又能虚灵不昧地具众理而应万事,心性二者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牟先生的修改以得于天者是理,虚灵不昧是心,是以心性截然二分的方式来理解明德注。以此一心性二分的格局来说明明德注,虽然很清楚,但不太能表达朱子上文所论明德是“心性相关联,不一不二”之意,亦不能表示明德之“明”未尝息之义。牟先生之修改是见到明德注中似乎以虚灵不昧为主词,但又以性理为实践的客观根据,会产生明德是说心或者是说性的问题,而且如果以明德为心,则心可能就可以往心即理来理解,这不合朱子原意。于是根据他所理解的朱子是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架构,确定的以“性理”为明德,而“虚灵不昧”是心所以能够统摄理的能力,于是明德注就符合心性为二,以心的认知统摄性理而应万事之义,于是就去掉了明德注中原文所含有的心性或心性情本来就先验的相关联之义。牟先生的修改虽然明白,但可能已经把明德注本来含有的一些意思去掉了。
明德以理为主,或甚至直接说是理,如牟先生所说,于朱子文献也有根据,是可以说的。但这明德何以是光明昭著?则必须说此性理是在心中的理,由于在心中,故表现了光明昭著的意义。如上文所说,这里便须有心与理密切的关联在一起而分不开之意。不必如牟先生对朱子注语所作的修正,而明确的规定心性为二,即明德为性理,而由心之认知来关联之,这可以多引一些朱子的原文来说明。在上文已引的明德注中,朱子说:
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
文中明确表示明德之明,是“本体之明”,即其明是人人本具、不会丧失的。于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这明德的流露,而充分实现其明,这即是恢复了明德的本体。如果明德只就性理来说,就不容易表示其是“未尝息”的本体之明之意。因为如果是心理为二,心要通过后天的认知才知道性理,则心对于性理的明白是后天产生的,不能说是本体之明,也不能说是此明未尝息。因此如果要满足此注文之文意,必须肯定性理必可以光明地表现出来,而性理的光明与虚灵不昧的心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此则必须说明德是心与性的连接才可以表现其明,故心的知性,或通过心知而把性理光明地表现出来,就有先验性。此即是说人人都本有这种对于性理的了解,性理在人心中都能光明地表现出来。这应该是朱子的明德注所表达的本意,即心性固然为二,但“心性关连而成”的明德,是有本体的性格的。此本体之明是人人都有的,不会丧失的。《朱子语类》对此有如下的讨论:
此是本领,不可不如此说破。②
此条《大学纂疏》置于“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下。
又曰: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③
按所谓“本领”即是内圣成德的根据,问题是这根据是经验的,还是超越的(先验的)?根据第二条所说“终是遮不得”,可见此明德在日常生活中是随时可以表现出来的,也是人人都可能理解的。故这成德的根据应该是超越的。这才能与“本体之明”之意相应,而若如是,则所谓本领便是成德的超越根据。《语录》又载:
明德未尝息,时时发见于日用之间,如见非义而羞恶,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尊贤而恭敬,见善事而叹慕,皆明德之发见也。如此推之极多。④
朱子如此解“明德未尝息”,是表示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感受到、或认知到性理与道德的意义,这一种对理的知与感受,是人随时都有的。这可以证上文“明德”不能只从性理来说之意。退一步说,若只以理说明德,也可以推出此理发见于日用,而为人心所易知之义。这亦可以证明朱子所说的明德是从人对于道德之理的本知或常知来说,此人对道德之理的知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是可以在生活经验上给出证明的。朱子又说:
人之明德,未尝不明,虽其昏蔽之极,而其善端之发,终不可绝,但当于其所发之端,而接续光明之,则其全体可以常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这里便明将去。①
从“昏蔽之极”的人也有明德之发,可证上文所说的此明是本体之明,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发这种道德的明觉之义。虽然这明德不是心即理的本心,而为心与性理的相关联,但由于是人人都有的本体之明,则心知与理的关联就必须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关联。故心之知性理,可说是先验的知识或“理性的知识”,此知识并非由经验而来。朱子的明德注,有“人之所得乎天”一句,说这是人所得于天的,就表示了这明德是先验的。而如果明德可以从心对于理本有之知来说,则这种知当然也可以说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而由于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则就可以理解何以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是很容易的,一般人都能有的。如上文所说,人一旦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反省,要求自己的行动是道德的行动,那就会很容易看到怎么样的存心给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此意是说,人一旦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要求自己给出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时,他就会以我这行为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做,我这行为的动机或存心是否为人人都该有的动机或存心来反问自己。只要人作出这种道德性的反省,就会按照行为的存心(行动的主观原则)是否为可普遍的,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为道德行为。虽然此意如果要充分展开,或要说明道德法则的全幅内容,并不容易,如康德之分析。但上述的关于何谓道德的理解,人人都有,而且都很恰当,一般人都能够以道德的行为是普遍而必然的,并不出于个人私利之动机来衡量或判断行为是否为道德、是否有道德的意义,这种对道德的本知与常知,是人人都有的经验。是以朱子对明德的了解,如上文所引的文献所说,应该是合理的。人对道德的理解有本知与常知,顺此知而展开之,便可对道德之义作进一步之理解。如“普遍性”与“必然性”是道德法则之特性,不能认为人主观的、偶然的、可容许有例外的作为是道德的行为;又如孟子所说的“义利之辨”,即道德是无条件地为义而行的行为,且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从道德行为只能是为了义所给出的行为,便须肯定义内,即道德法则是人的意志自己给出的。以上对道德的说明,虽然不算详细,但意义已很深切,是一般人都有的道德意识所含的,是很明白的。一般人都用这对道德的认识或其中所含的原理,来鉴别什么是道德行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或道德上的对错是非。这种道德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固然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很清楚,但不表示我们能无例外地或自然地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做,道德行为所要求的无条件性,我们现实上的意志、行动的主体往往不能企及。我们在服膺义务的时候固然知道应该为义务而义务,但是同时我们又会想借着义务的行为得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是康德所说“自然的辩证”之意,这一生命的问题,是从事实践必会遇到、必须加以解决的。因此对于这个道德之理的了解虽然容易,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实践并不容易,但不妨碍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实。我想这应该就是“明德”之所以是“明”之意。就是说德性的道理,人只要稍加反省,要求自己能够遵循“应该”而行动,就可以明白。此明德之明亦可从道德之理十分特别或奇特上说。道德之理是以定然令式来表示的,要人无条件行所当行,它不会用现实上的好处、感性上之满足来吸引人,但就足以令人不得不信服,而且努力去遵守。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特别。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有所为而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考虑、算计再给出行动,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何谓道德行动时,就要把所有考虑、算计抛掉,而无条件的只因为是义的缘故而行,这样的要求行动的存心必须是纯粹的道理或原则,是我们自己认为当该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不得不惭愧、内疚。这一种如此特别的道理非常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心中。因此,虽然明德是要通过我们的心知的理解力,才能清楚地为我们所认识,但我们一旦理解或认识到道德之理时,就会肯定这个道理实在十分清楚、明白,是不容置疑的,于是“明”也必须是道德之理本具的特征,即光明昭著是道德之理本身的特性。德性之理本来就是清楚明白,所以很容易被了解,不同于人通过后天经验而认识到的,有关世界的种种知识道理。我想朱子在界定明德时,一定是考虑到道德之理具备上述的特征,而以此特征来理解明德的“明”之意义。明德是指道德之理,即性理,而由于道德之理有上述清楚、明白,又容易被知的性格,所以可以说明德,又可以说虚灵不昧。虚灵虽然是从心知的作用讲,但不昧是重在性理上说的,即是说对于这种非常清楚明白,人不能不承认的道理,是不能够硬说不明白的,即此理是不容自昧的。对于这个道理你若说不明白,那就是自昧甚至是自欺了。但这一种对于性理的清楚明白,只能是上文所说的常知,而不是真知。必须根据此常知进一步对性理做彻底的了解,才可以说是真知。能真知理就能够诚意。所谓诚意,如同朱子在诚意处的注解:“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①所谓“一于善”是把道德上的善作为自己一心一意的行为目标,也可以说是为了善而为善,没有想到为了其他,而这样才可以说是无自欺,就可以无例外地给出道德行为。此即要自己的心完全合于理。
如果此说可通,则明德是性理在于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在心知中,于是这性理本身清楚明白,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看到这理的彰显。人只要反省一下自己对行动存心的要求,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这理的存在。这样讲明德,就表达了人有一种无论是智或愚都能有的对德性的清楚了解,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固然这个根据不是本心,不能如同陆王之学因为觉悟本心就畅通人的德性根源,而给出道德的行为,但亦有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伊川朱子不能如陆王般直接的承体起用,而必须根据这种本有的、对道德的了解作进一步的了解。要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是需要推致心知的作用,但不能够因为朱子重视后天的以心知知理的作用,就说心与理之二是截然为二,理不是心所本知、本具,而且即使心知理,理也只能是所知的对象,不能反身而成为实践道德的动力。推致心知,亦是推致知中之理,亦可说知与理在致知中同时彰显。故可以说,朱子致知格物的道学问工夫是有先天或先验之根据者。
如此的理解明德,我认为可以说明朱子在明德注中所说“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之意,如果像牟先生所说明德是理,则明德何以不论是智愚都未尝息呢?而且明德是本体之明,即是说人人都有此“明”,而且是不会丧失的。这种本体之明当然必须关联到心知来说,虽然关联到心知,但也必须表示这种心知之明是本有的,此明并不是只就心的认识作用来说,而是就对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即上文所说的常知。人人都有这种对于道德之理一般的了解,一反省就显明出来,谁也不能自昧,于是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明,是就本来就了解理来说的,即“知”不只是理解力或认识能力,而是对理有本来的认识了解。故当朱子说:“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①时,这个知所识的是理,知与理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致知是就心知对于理的本来了解推而致之。虽然“致知在格物”是表示心知要通过对事事物物的穷格,才可以对理有充分的了解,但这是在以心本知理为基础下,通过格物而要求对理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可以这样说,则格物致知的确如朱子《大学章句·格致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此所谓已知之理,是就上文所说的对于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如果可以这样解说,则格物致知是从对于道性理一般的了解进至极致的了解。并不是在不知理的情况下,通过穷格事物之理而取得道德之理的知识。
是故依朱子之说统,其在《大学》中关于明德所作之注语实当修改如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可以由虚灵不昧之心知之明以认知地管摄之”之光明正大之性理之谓也。如此修改,不以“虚灵不昧”为首出之主词,省得摇转不定,而亦与朱子之思想一贯。若如原注语,则很易令人误会为承孟子而来之陆王之讲法。①
牟先生这样修改,就确定地把明德规定为“人所得于天的光明正大的性理”,即“明德”只就性理来说。而虚灵不昧专是就心而言,人的心知以其本有的,虚灵不昧的认知能力管摄性理。如此理解明德,则固然清楚区分心性为二,但亦突显心的知理是通过后天的认识而知之义,于是心的知理是没有保证的,人的心知可以知理也可以不知理。经过牟先生这样明确的规定,朱子论明德时,有些意思就似乎被淘汰掉了。如上文所说的,朱子在论明德时心与性是分不开的,“说一个,另一个随到”,依照朱子这些话,心与性在明德处是分不开的。如果二者是分不开的,则可以说是有先验的关联性。另外,明德的作用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此就表示了心统性情之义。心具众理是应万事的根据,故心管摄性理就能够应万事,能应万事是心统性的作用,而应万事的活动就表现了情,故朱子论明德包含了心统性情之义。以此为明德,则心统性情亦是心本有的性能,即心之虚灵本来便可具众理而表现四端来应万事,此心性情三者,在明德中本来是关联在一起的。或可说,由于这三者本来就相关联,于是总起来说明德。如果此说可通,则就不能说心要通过后天的经验认知,才可以关联性理,而表现为四端之情。若依牟先生对“明德注”之修改,心统性情是心之功能,并不能归诸明德。①即不能从明德说心统性情,心的统性情的作用,是通过心知的后天的作用。如此一来,便削弱了以此明德为人人本具的本体之明之义。即心之虚灵的作用是明德本具的,故曰:“心之体用本来如是”,此明是人人原则上有的、本具的妙用,如果这种作用充分发挥,就是心的“全体大用”,所谓心的全体大用,应该是就实现心本来的知理之明,表现心统性情的作用。如果是心通过后天的认知作用而关联到性理,则此妙用及明理之“本来如是”,即本然义,便去掉了。
故牟先生对“明德注”的修改固然很清楚地表达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朱子见解,但以此来解释明德注,则心须通过后天经验的认知作用,才能知理,依理而行,此是后天之渐教,心知理及依理而行,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心之知理是须通过格物穷理以知之,从存在之然之曲折处明善,即从善之事物处明其所以然,这是从“然”以知其“所以然”,这亦不能保证能知道德之理。但牟先生此释于朱子文意,似不甚顺适。因为明德注的原文相当清楚地表示明德是人所得于天,是人人本来便有,而又能虚灵不昧地具众理而应万事,心性二者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牟先生的修改以得于天者是理,虚灵不昧是心,是以心性截然二分的方式来理解明德注。以此一心性二分的格局来说明明德注,虽然很清楚,但不太能表达朱子上文所论明德是“心性相关联,不一不二”之意,亦不能表示明德之“明”未尝息之义。牟先生之修改是见到明德注中似乎以虚灵不昧为主词,但又以性理为实践的客观根据,会产生明德是说心或者是说性的问题,而且如果以明德为心,则心可能就可以往心即理来理解,这不合朱子原意。于是根据他所理解的朱子是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架构,确定的以“性理”为明德,而“虚灵不昧”是心所以能够统摄理的能力,于是明德注就符合心性为二,以心的认知统摄性理而应万事之义,于是就去掉了明德注中原文所含有的心性或心性情本来就先验的相关联之义。牟先生的修改虽然明白,但可能已经把明德注本来含有的一些意思去掉了。
明德以理为主,或甚至直接说是理,如牟先生所说,于朱子文献也有根据,是可以说的。但这明德何以是光明昭著?则必须说此性理是在心中的理,由于在心中,故表现了光明昭著的意义。如上文所说,这里便须有心与理密切的关联在一起而分不开之意。不必如牟先生对朱子注语所作的修正,而明确的规定心性为二,即明德为性理,而由心之认知来关联之,这可以多引一些朱子的原文来说明。在上文已引的明德注中,朱子说:
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
文中明确表示明德之明,是“本体之明”,即其明是人人本具、不会丧失的。于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这明德的流露,而充分实现其明,这即是恢复了明德的本体。如果明德只就性理来说,就不容易表示其是“未尝息”的本体之明之意。因为如果是心理为二,心要通过后天的认知才知道性理,则心对于性理的明白是后天产生的,不能说是本体之明,也不能说是此明未尝息。因此如果要满足此注文之文意,必须肯定性理必可以光明地表现出来,而性理的光明与虚灵不昧的心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此则必须说明德是心与性的连接才可以表现其明,故心的知性,或通过心知而把性理光明地表现出来,就有先验性。此即是说人人都本有这种对于性理的了解,性理在人心中都能光明地表现出来。这应该是朱子的明德注所表达的本意,即心性固然为二,但“心性关连而成”的明德,是有本体的性格的。此本体之明是人人都有的,不会丧失的。《朱子语类》对此有如下的讨论:
此是本领,不可不如此说破。②
此条《大学纂疏》置于“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下。
又曰: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③
按所谓“本领”即是内圣成德的根据,问题是这根据是经验的,还是超越的(先验的)?根据第二条所说“终是遮不得”,可见此明德在日常生活中是随时可以表现出来的,也是人人都可能理解的。故这成德的根据应该是超越的。这才能与“本体之明”之意相应,而若如是,则所谓本领便是成德的超越根据。《语录》又载:
明德未尝息,时时发见于日用之间,如见非义而羞恶,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尊贤而恭敬,见善事而叹慕,皆明德之发见也。如此推之极多。④
朱子如此解“明德未尝息”,是表示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感受到、或认知到性理与道德的意义,这一种对理的知与感受,是人随时都有的。这可以证上文“明德”不能只从性理来说之意。退一步说,若只以理说明德,也可以推出此理发见于日用,而为人心所易知之义。这亦可以证明朱子所说的明德是从人对于道德之理的本知或常知来说,此人对道德之理的知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是可以在生活经验上给出证明的。朱子又说:
人之明德,未尝不明,虽其昏蔽之极,而其善端之发,终不可绝,但当于其所发之端,而接续光明之,则其全体可以常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这里便明将去。①
从“昏蔽之极”的人也有明德之发,可证上文所说的此明是本体之明,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发这种道德的明觉之义。虽然这明德不是心即理的本心,而为心与性理的相关联,但由于是人人都有的本体之明,则心知与理的关联就必须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关联。故心之知性理,可说是先验的知识或“理性的知识”,此知识并非由经验而来。朱子的明德注,有“人之所得乎天”一句,说这是人所得于天的,就表示了这明德是先验的。而如果明德可以从心对于理本有之知来说,则这种知当然也可以说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而由于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则就可以理解何以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是很容易的,一般人都能有的。如上文所说,人一旦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反省,要求自己的行动是道德的行动,那就会很容易看到怎么样的存心给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此意是说,人一旦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要求自己给出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时,他就会以我这行为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做,我这行为的动机或存心是否为人人都该有的动机或存心来反问自己。只要人作出这种道德性的反省,就会按照行为的存心(行动的主观原则)是否为可普遍的,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为道德行为。虽然此意如果要充分展开,或要说明道德法则的全幅内容,并不容易,如康德之分析。但上述的关于何谓道德的理解,人人都有,而且都很恰当,一般人都能够以道德的行为是普遍而必然的,并不出于个人私利之动机来衡量或判断行为是否为道德、是否有道德的意义,这种对道德的本知与常知,是人人都有的经验。是以朱子对明德的了解,如上文所引的文献所说,应该是合理的。人对道德的理解有本知与常知,顺此知而展开之,便可对道德之义作进一步之理解。如“普遍性”与“必然性”是道德法则之特性,不能认为人主观的、偶然的、可容许有例外的作为是道德的行为;又如孟子所说的“义利之辨”,即道德是无条件地为义而行的行为,且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从道德行为只能是为了义所给出的行为,便须肯定义内,即道德法则是人的意志自己给出的。以上对道德的说明,虽然不算详细,但意义已很深切,是一般人都有的道德意识所含的,是很明白的。一般人都用这对道德的认识或其中所含的原理,来鉴别什么是道德行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或道德上的对错是非。这种道德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固然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很清楚,但不表示我们能无例外地或自然地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做,道德行为所要求的无条件性,我们现实上的意志、行动的主体往往不能企及。我们在服膺义务的时候固然知道应该为义务而义务,但是同时我们又会想借着义务的行为得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是康德所说“自然的辩证”之意,这一生命的问题,是从事实践必会遇到、必须加以解决的。因此对于这个道德之理的了解虽然容易,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实践并不容易,但不妨碍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实。我想这应该就是“明德”之所以是“明”之意。就是说德性的道理,人只要稍加反省,要求自己能够遵循“应该”而行动,就可以明白。此明德之明亦可从道德之理十分特别或奇特上说。道德之理是以定然令式来表示的,要人无条件行所当行,它不会用现实上的好处、感性上之满足来吸引人,但就足以令人不得不信服,而且努力去遵守。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特别。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有所为而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考虑、算计再给出行动,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何谓道德行动时,就要把所有考虑、算计抛掉,而无条件的只因为是义的缘故而行,这样的要求行动的存心必须是纯粹的道理或原则,是我们自己认为当该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不得不惭愧、内疚。这一种如此特别的道理非常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心中。因此,虽然明德是要通过我们的心知的理解力,才能清楚地为我们所认识,但我们一旦理解或认识到道德之理时,就会肯定这个道理实在十分清楚、明白,是不容置疑的,于是“明”也必须是道德之理本具的特征,即光明昭著是道德之理本身的特性。德性之理本来就是清楚明白,所以很容易被了解,不同于人通过后天经验而认识到的,有关世界的种种知识道理。我想朱子在界定明德时,一定是考虑到道德之理具备上述的特征,而以此特征来理解明德的“明”之意义。明德是指道德之理,即性理,而由于道德之理有上述清楚、明白,又容易被知的性格,所以可以说明德,又可以说虚灵不昧。虚灵虽然是从心知的作用讲,但不昧是重在性理上说的,即是说对于这种非常清楚明白,人不能不承认的道理,是不能够硬说不明白的,即此理是不容自昧的。对于这个道理你若说不明白,那就是自昧甚至是自欺了。但这一种对于性理的清楚明白,只能是上文所说的常知,而不是真知。必须根据此常知进一步对性理做彻底的了解,才可以说是真知。能真知理就能够诚意。所谓诚意,如同朱子在诚意处的注解:“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①所谓“一于善”是把道德上的善作为自己一心一意的行为目标,也可以说是为了善而为善,没有想到为了其他,而这样才可以说是无自欺,就可以无例外地给出道德行为。此即要自己的心完全合于理。
如果此说可通,则明德是性理在于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在心知中,于是这性理本身清楚明白,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看到这理的彰显。人只要反省一下自己对行动存心的要求,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这理的存在。这样讲明德,就表达了人有一种无论是智或愚都能有的对德性的清楚了解,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固然这个根据不是本心,不能如同陆王之学因为觉悟本心就畅通人的德性根源,而给出道德的行为,但亦有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伊川朱子不能如陆王般直接的承体起用,而必须根据这种本有的、对道德的了解作进一步的了解。要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是需要推致心知的作用,但不能够因为朱子重视后天的以心知知理的作用,就说心与理之二是截然为二,理不是心所本知、本具,而且即使心知理,理也只能是所知的对象,不能反身而成为实践道德的动力。推致心知,亦是推致知中之理,亦可说知与理在致知中同时彰显。故可以说,朱子致知格物的道学问工夫是有先天或先验之根据者。
如此的理解明德,我认为可以说明朱子在明德注中所说“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之意,如果像牟先生所说明德是理,则明德何以不论是智愚都未尝息呢?而且明德是本体之明,即是说人人都有此“明”,而且是不会丧失的。这种本体之明当然必须关联到心知来说,虽然关联到心知,但也必须表示这种心知之明是本有的,此明并不是只就心的认识作用来说,而是就对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即上文所说的常知。人人都有这种对于道德之理一般的了解,一反省就显明出来,谁也不能自昧,于是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明,是就本来就了解理来说的,即“知”不只是理解力或认识能力,而是对理有本来的认识了解。故当朱子说:“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①时,这个知所识的是理,知与理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致知是就心知对于理的本来了解推而致之。虽然“致知在格物”是表示心知要通过对事事物物的穷格,才可以对理有充分的了解,但这是在以心本知理为基础下,通过格物而要求对理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可以这样说,则格物致知的确如朱子《大学章句·格致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此所谓已知之理,是就上文所说的对于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如果可以这样解说,则格物致知是从对于道性理一般的了解进至极致的了解。并不是在不知理的情况下,通过穷格事物之理而取得道德之理的知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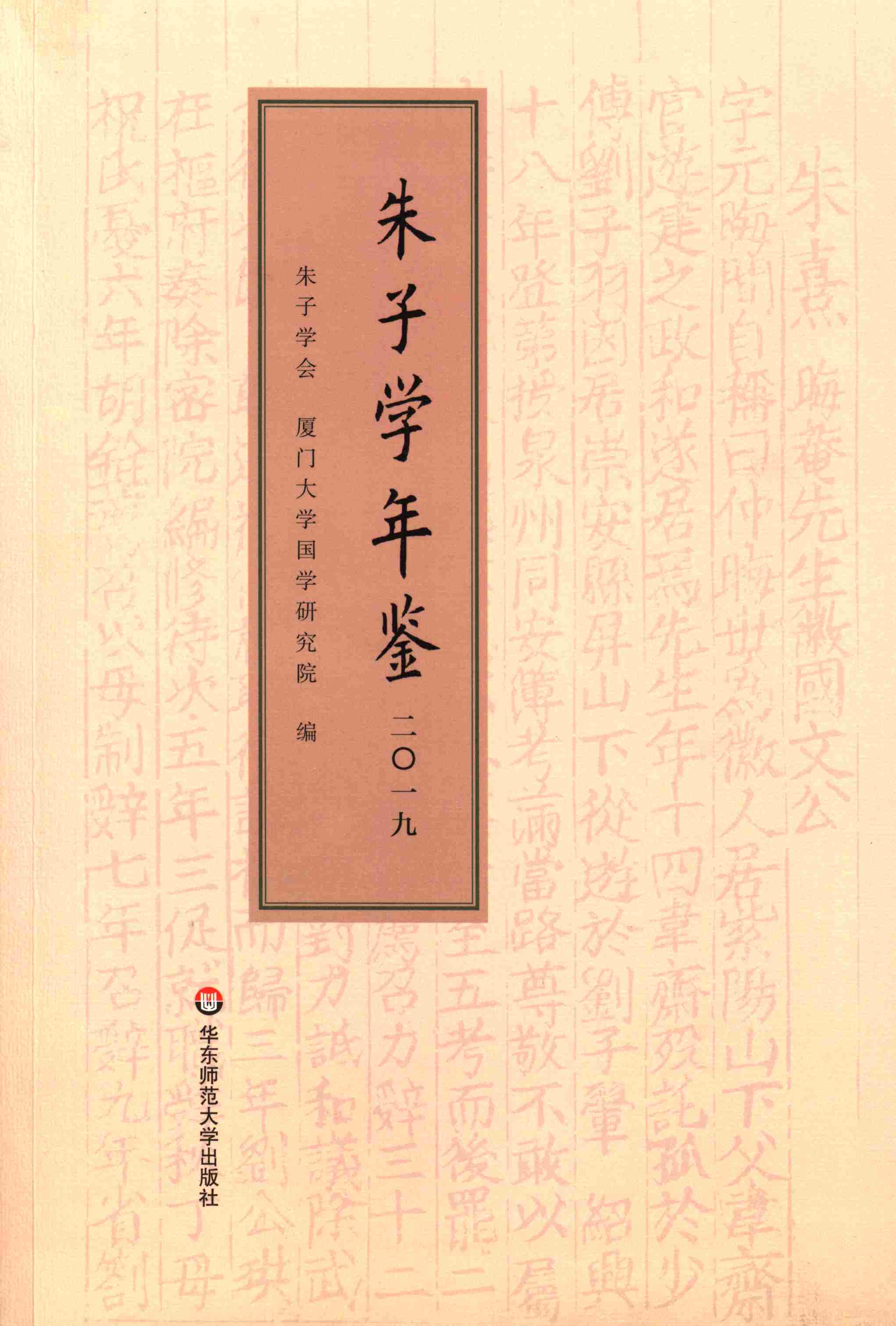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