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川、朱子可能是从横起纵的实践理论型态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898 |
| 颗粒名称: | 一、伊川、朱子可能是从横起纵的实践理论型态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5 |
| 页码: | 063-067 |
| 摘要: | 朱子非常看重《大学》,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明白的文章。他根据《大学》的内容,提出了儒学成德之教的程序,并对《大学》进行了详细的诠释和讨论。朱子的解读对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士人修养的标准教法。虽然近年来对朱子学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大多数人仍将他视为儒学的正宗。牟宗三对朱子的解释与传统朱子学有一定距离,因此对他的解释仍存在讨论。近年来,我通过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比较,对程伊川和朱子的理论进行了一些新的解读。康德认为必须从一般理性了解进入哲学性的了解,才能抵挡人们随感性之欲求而产生的“自然弯曲”。这正好说明了伊川和朱子追求真知的目标和必要性。康德认为要应对这种自然弯曲,避免道德的堕落,必须将道德法则从一般经验中抽离出来,并明确其作为先验普遍性的原理。程朱的格物穷理就是从人们对道德的本知、常知出发,进一步深入理解道德的理,并达到真切的理解的过程。因此,我认为程朱的理论并非像牟宗三所说的儒门别子,而是和陆王一样,同样是儒学中必备的一种成德理论。虽然二者有主理和主心的不同,但它们是可以相通的。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大学》 |
内容
朱子对《大学》十分看重,认为在他一生中,看得最明白的文章就是《大学》①。他借《大学》的三纲八目的内容,给出了儒学成德之教的工夫程序,固然这一设计与铺陈是根据《大学》文本,及承继了程伊川的讲法,但朱子的发明很多。他对《大学》的诠释及有关讨论,纲举目张,很清楚地表达实践成德的工夫与程序,及其根据。朱子此解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可说是南宋以后普遍成为士人作修养工夫的标准教法。虽然对于朱子学的诠释,近世由于牟宗三先生“别子为宗”的衡定,使朱子的思想理论比较不像过去,虽有朱陆异同,及王学盛行,仍无异议地被视为儒学的正宗。但牟先生的朱子诠释也很明显与过去八百年中国乃至于东亚社会尊崇朱子的事实有距离,于是,对于牟先生的诠释,当代是不断有商榷的意见提出的,只是大多数的反对意见不能有严格的哲学论证与对朱子文献的明白诠释作根据,对牟先生的说法于是便不能有所撼动。我近年对此作了一些思考,借着与康德之道德哲学比较,对伊川、朱子的理论型态作了一些新诠。康德肯定通常的理性(一般人)对道德法则有正确的了解,但必须从对法则的一般了解进到哲学的了解,才可以挡住人随顺感性之欲求,对要求人无条件地践德之道德意识给出挑战,而生起的“自然的辩证”②;此意正好可以说明伊川、朱子致知以求真知之义,即说明此主张的用心及其必要性。康德认为对付这自然的辩证,避免人道德的堕落,必须将道德法则从一般经验中抽出来,而明其为先验普遍之理。这一分析,即说明道德法则是根于纯粹理性的。此一康德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或对道德之根本原理的说明,亦如同伊川、朱子对性理之分解,即严格区分心性、理气有形上形下之异之作法。由此可见,程朱的格物穷理,是从人本来便有的对道德之理之了解(本知、常知),进至对道德之理有真知、切感的地步,故由格致可以达致诚意的结果。由是我认为程朱之义理型态并非如牟先生所说为儒门别子,而是可以与陆王并立,同为儒学应有,或甚至必须有的一个成德理论。二系虽有主理及主心的不同,但亦可以会通。③
如果上说可通,则对于牟先生的朱子诠释,我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一)朱子虽然清楚区分心、理为二,但并非表示心对于理本无所知,而要通过格物,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然出发追问其所以然的方式,才能了解性理。依朱子可以是认为人对于理本有所知,只是必需从一般的了解进到真知,于是将本知之理抽出来作进一步的理解;格物致知,便是以此本知之理为根据而作进一步求知之工夫。常知与真知之不同,如同康德所说的“对道德的一般理性的理解与哲学的理性的理解”之不同,伊川云:
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①
这一段所说的常知与真知,当然是就对道德之了解,而不是泛就一般知识上说。这从“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之语可知。故常知与真知,即普通的理解与深切的理解的不同,是专就对道德的理解的不同层次给出之区别。文中所谓的三尺童子莫不知虎能伤人,是譬喻对于何谓道德的善恶是非,是人所共知的;而以谈虎色变来形容的真知,是指对于本有了解的道德之理,达至真切了解的地步。能真知就自然能“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②
(二)如果程朱通过格物穷理所了解的理是道德之理,而且对此理有正确的了解,则在了解理的过程中,便会回过头来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要按理而行;或严格地讲,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只因为理、义的缘故而给出。此是说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并不同于认知对象般,只给出了对对象的客观的了解,而不必影响行动的主体之态度;在理解道德之理的过程中,由于是就本知之道德之理、应然之理进一步求了解,在不断深化了解中,也就深化了此理对自己行动的主体的要求,即必须要只因为理、义之故而行动。若是则程朱的致知穷理并不如牟先生所说,心与理的关系只是主客的横摄的、认知的关系,即理只能是客而不是主,是所而不是能(“以成其能所之二,认知关系之静摄”③),而应该是在不断深化对于理之知的时候,体证到理是我本有的,是我认可而必须要依之而实践的,这可以说是格物致知之后要反求诸己。理在致知之过程中逐渐成为心要依循的原则,终至心、理为一。程伊川便对格物穷理之后必须“反躬”(《礼记·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即反身以求,回到自己,以实践此理)给出了说明: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①
由此段可证,伊川是认为明理的过程也就是证明“理是我的理”之过程,愈明理,人就愈能反躬而自得。明于外,有证实此理本来是我之理的效果。故伊川亦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程氏遗书》卷18)。言理为我本有,既表示了此理是我本知,又表示了此理是我肯定的。对于道德之理,人一旦理解,便会有以上的感受,因为道德之理是理所当然的,越了解其为当然,便越发会肯定,亦越会产生要依此理以实践的要求。如果可以这样说,则致知以格物穷理,是以自己本有的,对道德之理的常知作根据,作进一步的探究,而达到真知的地步。到了真知理,便可以认为此理为我所有,是我所必须肯定,而且必须实践,有真切的要求;于是这种把理当作对象,以心知来深化、了解的活动,虽然是以横摄的认知性的活动而开始,但最后会以反求诸己,给出按性理而行的,也可以说是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让无条件的为义务而义务的实践具体给出来,那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行的,是我自己自发的要求自己按理而行的,这可以说是纵贯的活动。按理而行,似是横摄的活动,但若此理是我本知,越知而越加肯定,且视为我之理,而且要按理而实践,则亦是自发的,由我决定之行为,而这便是纵贯的。即此时之道德行为,虽然是按理而行,但理是我自己肯定的、自发的去依循的理,不是外在的理,故可说亦是意志之自我立法给出的。亦可说是“性发”,而且是“不容已”的。这是上文伊川所说“反躬”及“物我一理”之说可涵之义。故致知明理而诚意反躬,可以说是从横摄而起纵贯的活动。这种从横起纵的活动,在横摄处说,有主客二分、心理为二的情况,但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活动。一般的认识活动成就的是有关对象的知识,不会因为认知而给出实践的活动,亦不会愈认识而愈证此理为我本有。故可以说这对理之本知、常知,是和依此理而实践相关联的,此对理之知对意志是有要求的,即要求其作去妄存诚之工夫,要主体依理而行,并不能只看作单纯的认知。由于对理有所知,便会有依此理而行动的要求,而若不依此理而行,自己内心一定会感受到不安。如果对于道德法则的认知会有这种效果,则增加明理的程度,就自然会有实践要求的加强。牟先生认定了程朱的心与理为二、以心明理,只能是横摄的认知活动,实践的动力是不能给出来的。如果按上文所说,则牟先生这一论定是可以再商榷的。而人是否可能从对道德法则的清楚了解,而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呢?吾人认为是可以的,这除了上面的论述外,又可以用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互相涵蕴”之论来帮助说明:
这样,“自由”与“一无条件的实践法则”是互相涵蕴的。现在,在这里,我不问:是否它们两者事实上是不同的,抑或是否一个无条件的法则不宁只是一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而此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又是与积极的自由之概念为同一的;我只问:我们的关于“无条件地实践的东西”之知识从何处开始,是否它是从自由开始,抑或是从实践的法则开始?①
这是所谓康德的“交互论”②,由对道德法则的了解与分析,必须肯定人有意志之自由。由对自由的分析,可知自由意志所遵守的法则是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或说自由是道德法则之存在根据,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根据,故曰二者相涵蕴。既然道德法则与自由是“互相涵蕴(互相回溯)”的,则通过对道德法则的深切了解,就会意识到只因为法则的缘故,或被法则直接决定的意志,是人在从事道德的实践时必须要有的。若是则对于道德法则的了解,就会产生纯净化自己意志(力求存心之纯粹)而给出道德行动的要求,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从横起纵”的理论根据,这表示的对道德法则的认识,是从本来有的常知而进至真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要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的要求。这在人的日常心理,也是常见的事实。固然人不一定能给出存心纯粹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要求纯粹依理而行,要求行动的意志纯粹,是人驱之不去的道德的关切。既然有此关切,则对道德行为的加深了解,自然会相应而生起按道德法则而行的自我要求。那么伊川与朱子所主张的,必须以心明理、格物致知的作法为先,固然是横摄,但并非止于对道德之理有认知上的清楚,而必须反躬实践。这种由对于理的真切了解而要求纯粹实践,应该是人常有的感受。如果此说可通,则牟先生对于程朱为横摄系统,陆王为纵贯系统的区分,固然不错,但这两个系统,是可以会通的。从程朱之横摄,可以给出纵贯的道德实践,而陆王肯定心即理,先给出从本心自发的、直贯的道德创造,也必须回过头来,对于此本心或良知中所含的道德之理,作充分的分解以求明白,如此オ可对治道德之存心因感性欲望之反弹而造成之自欺。不然行动的存心如果受感性影响而滑转的话,就容易以情识为良知,而有荡越放肆的流弊。若此说可通,则由程、朱的横摄,固然可以起纵贯;而由陆、王的纵贯,亦须回头作横摄的工夫。这两个系统也可以用《中庸》中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来类比,即明理可以诚身,而诚身也可以有明理的后果,两者是不能偏废的。诚明两进,才可以保证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也可以说是《中庸》的“交互论”。
如果上说可通,则对于牟先生的朱子诠释,我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一)朱子虽然清楚区分心、理为二,但并非表示心对于理本无所知,而要通过格物,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然出发追问其所以然的方式,才能了解性理。依朱子可以是认为人对于理本有所知,只是必需从一般的了解进到真知,于是将本知之理抽出来作进一步的理解;格物致知,便是以此本知之理为根据而作进一步求知之工夫。常知与真知之不同,如同康德所说的“对道德的一般理性的理解与哲学的理性的理解”之不同,伊川云:
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①
这一段所说的常知与真知,当然是就对道德之了解,而不是泛就一般知识上说。这从“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之语可知。故常知与真知,即普通的理解与深切的理解的不同,是专就对道德的理解的不同层次给出之区别。文中所谓的三尺童子莫不知虎能伤人,是譬喻对于何谓道德的善恶是非,是人所共知的;而以谈虎色变来形容的真知,是指对于本有了解的道德之理,达至真切了解的地步。能真知就自然能“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②
(二)如果程朱通过格物穷理所了解的理是道德之理,而且对此理有正确的了解,则在了解理的过程中,便会回过头来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要按理而行;或严格地讲,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只因为理、义的缘故而给出。此是说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并不同于认知对象般,只给出了对对象的客观的了解,而不必影响行动的主体之态度;在理解道德之理的过程中,由于是就本知之道德之理、应然之理进一步求了解,在不断深化了解中,也就深化了此理对自己行动的主体的要求,即必须要只因为理、义之故而行动。若是则程朱的致知穷理并不如牟先生所说,心与理的关系只是主客的横摄的、认知的关系,即理只能是客而不是主,是所而不是能(“以成其能所之二,认知关系之静摄”③),而应该是在不断深化对于理之知的时候,体证到理是我本有的,是我认可而必须要依之而实践的,这可以说是格物致知之后要反求诸己。理在致知之过程中逐渐成为心要依循的原则,终至心、理为一。程伊川便对格物穷理之后必须“反躬”(《礼记·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即反身以求,回到自己,以实践此理)给出了说明: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①
由此段可证,伊川是认为明理的过程也就是证明“理是我的理”之过程,愈明理,人就愈能反躬而自得。明于外,有证实此理本来是我之理的效果。故伊川亦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程氏遗书》卷18)。言理为我本有,既表示了此理是我本知,又表示了此理是我肯定的。对于道德之理,人一旦理解,便会有以上的感受,因为道德之理是理所当然的,越了解其为当然,便越发会肯定,亦越会产生要依此理以实践的要求。如果可以这样说,则致知以格物穷理,是以自己本有的,对道德之理的常知作根据,作进一步的探究,而达到真知的地步。到了真知理,便可以认为此理为我所有,是我所必须肯定,而且必须实践,有真切的要求;于是这种把理当作对象,以心知来深化、了解的活动,虽然是以横摄的认知性的活动而开始,但最后会以反求诸己,给出按性理而行的,也可以说是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让无条件的为义务而义务的实践具体给出来,那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行的,是我自己自发的要求自己按理而行的,这可以说是纵贯的活动。按理而行,似是横摄的活动,但若此理是我本知,越知而越加肯定,且视为我之理,而且要按理而实践,则亦是自发的,由我决定之行为,而这便是纵贯的。即此时之道德行为,虽然是按理而行,但理是我自己肯定的、自发的去依循的理,不是外在的理,故可说亦是意志之自我立法给出的。亦可说是“性发”,而且是“不容已”的。这是上文伊川所说“反躬”及“物我一理”之说可涵之义。故致知明理而诚意反躬,可以说是从横摄而起纵贯的活动。这种从横起纵的活动,在横摄处说,有主客二分、心理为二的情况,但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活动。一般的认识活动成就的是有关对象的知识,不会因为认知而给出实践的活动,亦不会愈认识而愈证此理为我本有。故可以说这对理之本知、常知,是和依此理而实践相关联的,此对理之知对意志是有要求的,即要求其作去妄存诚之工夫,要主体依理而行,并不能只看作单纯的认知。由于对理有所知,便会有依此理而行动的要求,而若不依此理而行,自己内心一定会感受到不安。如果对于道德法则的认知会有这种效果,则增加明理的程度,就自然会有实践要求的加强。牟先生认定了程朱的心与理为二、以心明理,只能是横摄的认知活动,实践的动力是不能给出来的。如果按上文所说,则牟先生这一论定是可以再商榷的。而人是否可能从对道德法则的清楚了解,而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呢?吾人认为是可以的,这除了上面的论述外,又可以用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互相涵蕴”之论来帮助说明:
这样,“自由”与“一无条件的实践法则”是互相涵蕴的。现在,在这里,我不问:是否它们两者事实上是不同的,抑或是否一个无条件的法则不宁只是一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而此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又是与积极的自由之概念为同一的;我只问:我们的关于“无条件地实践的东西”之知识从何处开始,是否它是从自由开始,抑或是从实践的法则开始?①
这是所谓康德的“交互论”②,由对道德法则的了解与分析,必须肯定人有意志之自由。由对自由的分析,可知自由意志所遵守的法则是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或说自由是道德法则之存在根据,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根据,故曰二者相涵蕴。既然道德法则与自由是“互相涵蕴(互相回溯)”的,则通过对道德法则的深切了解,就会意识到只因为法则的缘故,或被法则直接决定的意志,是人在从事道德的实践时必须要有的。若是则对于道德法则的了解,就会产生纯净化自己意志(力求存心之纯粹)而给出道德行动的要求,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从横起纵”的理论根据,这表示的对道德法则的认识,是从本来有的常知而进至真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要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的要求。这在人的日常心理,也是常见的事实。固然人不一定能给出存心纯粹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要求纯粹依理而行,要求行动的意志纯粹,是人驱之不去的道德的关切。既然有此关切,则对道德行为的加深了解,自然会相应而生起按道德法则而行的自我要求。那么伊川与朱子所主张的,必须以心明理、格物致知的作法为先,固然是横摄,但并非止于对道德之理有认知上的清楚,而必须反躬实践。这种由对于理的真切了解而要求纯粹实践,应该是人常有的感受。如果此说可通,则牟先生对于程朱为横摄系统,陆王为纵贯系统的区分,固然不错,但这两个系统,是可以会通的。从程朱之横摄,可以给出纵贯的道德实践,而陆王肯定心即理,先给出从本心自发的、直贯的道德创造,也必须回过头来,对于此本心或良知中所含的道德之理,作充分的分解以求明白,如此オ可对治道德之存心因感性欲望之反弹而造成之自欺。不然行动的存心如果受感性影响而滑转的话,就容易以情识为良知,而有荡越放肆的流弊。若此说可通,则由程、朱的横摄,固然可以起纵贯;而由陆、王的纵贯,亦须回头作横摄的工夫。这两个系统也可以用《中庸》中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来类比,即明理可以诚身,而诚身也可以有明理的后果,两者是不能偏废的。诚明两进,才可以保证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也可以说是《中庸》的“交互论”。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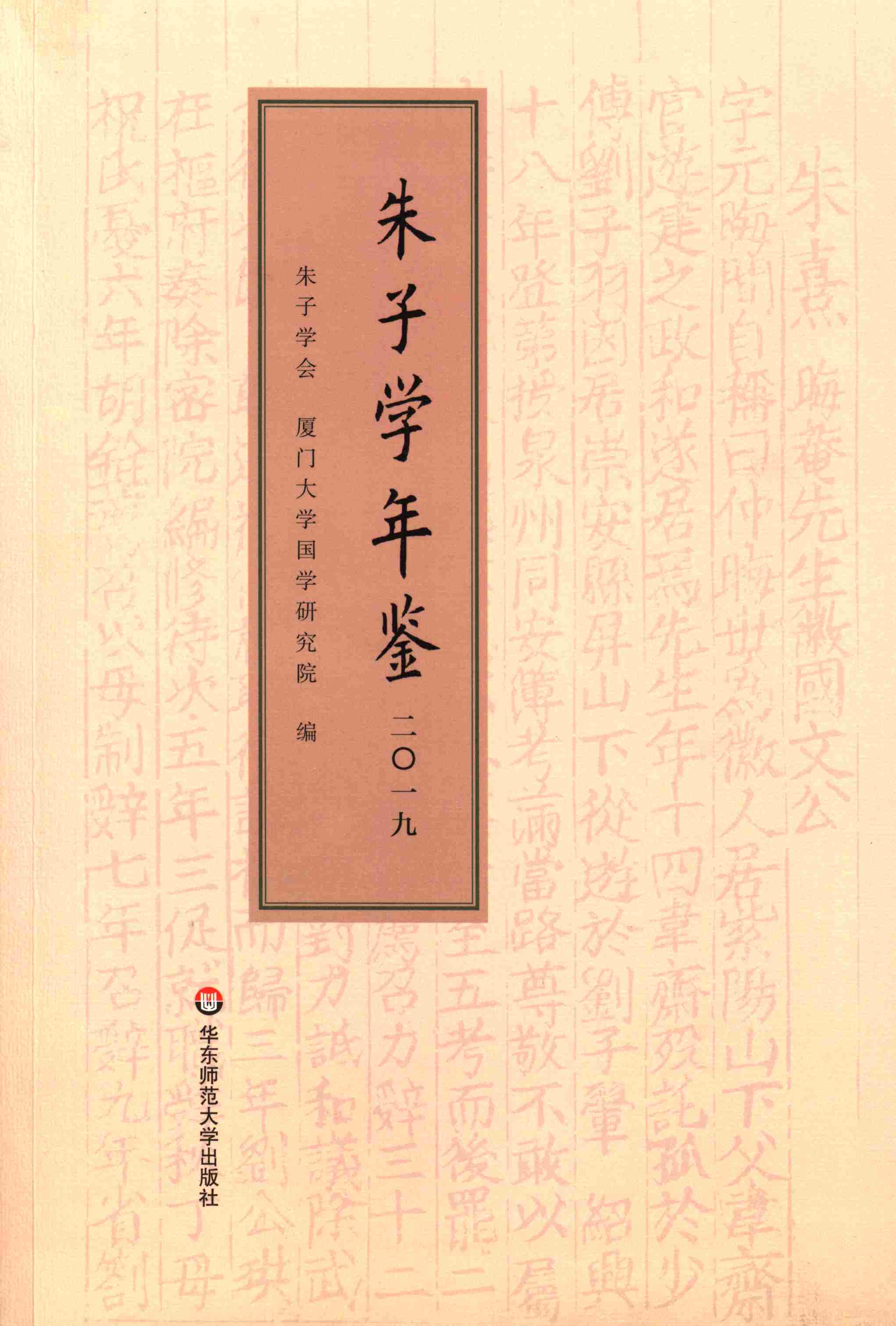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杨祖汉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