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明德注”新诠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897 |
| 颗粒名称: | 朱子的“明德注”新诠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20 |
| 页码: | 062-081 |
| 摘要: | 朱子对《大学》中的“明德”进行了注解,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有人认为明德是指心,有人认为是指性。牟宗三先生认为,按朱子的意思,明德是指性,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和修订。然而,通过研究朱子的相关文献,我认为明德涉及心性(理),性理在心中显现。明德不能单指心或理,而是两者相互关联。朱子认为,虽然不能说心即是理,但心是具有清晰知觉的虚灵,在这种“知觉”中本来就包含对道德理念的理解和认知。可以说,人对于道德和义务的理解是基于“理性之知识”的。只要人稍加反省自己的行为,就能理解行为所基于的道德法则或规律。朱子认为,这种对道德法则的认知是人无法否认的,不论气质如何,欲望如何,都不能自欺欺人。朱子虽然主张心和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并不否认心对于理的存在。这种对道德理念的“本知”或“常知”与朱子所理解的明德之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人之所以具有明德,是因为对于道德、仁义礼智等的本有认知。因此,“明德”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这正是人们能够运用理解,实现对道德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展现真正的道德行为的基础。因此,“明明德”是基于确认存在的“明德”(即对道德理念的本有认知)而进行的修行,所以这种“明明德”的修行是有先验基础的。总之,朱子的“明德注”是在肯定人对道德理念的本有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强调了通过进一步探究已有的认知来深化理解,因此朱子可以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而所谓“一旦豁然贯通”也有理论依据,这并非是“异质的跳跃”。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明德注 |
内容
朱子对《大学》“明德”的注解引发了当时及后代儒者许多的讨论,究竟明德是指心或是指性而言?在朱子的有关文献中都可以找出根据。当代牟宗三先生认为依朱子,明德是指性而言,对此他做了非常严谨明白的分疏,又对朱子的注文给出修订。笔者细探“明德注”与《大学或问》、《朱子语类》、《文集》的有关文献,认为明德是心性(理)相关联,而性理在心中呈现之意。明德不能单指心或理(性),而是两者关联在一起。依朱子,固然不能说心即是理,但心为虚灵明觉之知,在此“知”中,本来便有对道德之理的理解或知识存在。可以说,人对于何谓道德,何谓义务,是具有“理性之知识”者。人只要对自己的行为稍加反省,就可以理解到行为所依据的道德法则,或是非之律应该是什么。这种对道德法则或是非之律之知,朱子认为是人所不能否认的,不管人的气禀如何不理想,或欲望习气如何深重,也是不能自昧的。朱子虽然主张心与理为二,但并不否定心对理本有所知,对此朱子是有明确表示的。此种对道德之理的“本知”或“常知”与朱子所理解的明德之义,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可以说,人所以有明德,其理由便在于这对道德或仁义礼智的本有所知。因此“明德”是常常表现在日用生活中的,而这就是人能格物穷理,充分实现对于理的理解,由此而诚意,使人能有真正的道德行为的出现的根据。故“明明德”是在肯定本有的“明德”(即对于道德之理的本有之知)的情况下做工夫,于是此一明明德的工夫是有先验的根据的。此应该是朱子诠释明德的原意。本文准备证成此一对明德的理解,并引朱子的文献证明朱子在“明德注”中所说的“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是表示理在心中随时有其流露,故人对于道德之理是本有所知的。本着此对性理的本知或已知,就可以进一步而求真知,故朱子可以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而所谓“一旦豁然贯通”,便有理论上的根据,此是一超越(先验)的根据,故由致知而“豁然贯通”,并非“异质的跳跃”①。如此解释,应可以对朱子的成德理论给出一个较为顺当的说明。
一、伊川、朱子可能是从横起纵的实践理论型态
朱子对《大学》十分看重,认为在他一生中,看得最明白的文章就是《大学》①。他借《大学》的三纲八目的内容,给出了儒学成德之教的工夫程序,固然这一设计与铺陈是根据《大学》文本,及承继了程伊川的讲法,但朱子的发明很多。他对《大学》的诠释及有关讨论,纲举目张,很清楚地表达实践成德的工夫与程序,及其根据。朱子此解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可说是南宋以后普遍成为士人作修养工夫的标准教法。虽然对于朱子学的诠释,近世由于牟宗三先生“别子为宗”的衡定,使朱子的思想理论比较不像过去,虽有朱陆异同,及王学盛行,仍无异议地被视为儒学的正宗。但牟先生的朱子诠释也很明显与过去八百年中国乃至于东亚社会尊崇朱子的事实有距离,于是,对于牟先生的诠释,当代是不断有商榷的意见提出的,只是大多数的反对意见不能有严格的哲学论证与对朱子文献的明白诠释作根据,对牟先生的说法于是便不能有所撼动。我近年对此作了一些思考,借着与康德之道德哲学比较,对伊川、朱子的理论型态作了一些新诠。康德肯定通常的理性(一般人)对道德法则有正确的了解,但必须从对法则的一般了解进到哲学的了解,才可以挡住人随顺感性之欲求,对要求人无条件地践德之道德意识给出挑战,而生起的“自然的辩证”②;此意正好可以说明伊川、朱子致知以求真知之义,即说明此主张的用心及其必要性。康德认为对付这自然的辩证,避免人道德的堕落,必须将道德法则从一般经验中抽出来,而明其为先验普遍之理。这一分析,即说明道德法则是根于纯粹理性的。此一康德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或对道德之根本原理的说明,亦如同伊川、朱子对性理之分解,即严格区分心性、理气有形上形下之异之作法。由此可见,程朱的格物穷理,是从人本来便有的对道德之理之了解(本知、常知),进至对道德之理有真知、切感的地步,故由格致可以达致诚意的结果。由是我认为程朱之义理型态并非如牟先生所说为儒门别子,而是可以与陆王并立,同为儒学应有,或甚至必须有的一个成德理论。二系虽有主理及主心的不同,但亦可以会通。③
如果上说可通,则对于牟先生的朱子诠释,我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一)朱子虽然清楚区分心、理为二,但并非表示心对于理本无所知,而要通过格物,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然出发追问其所以然的方式,才能了解性理。依朱子可以是认为人对于理本有所知,只是必需从一般的了解进到真知,于是将本知之理抽出来作进一步的理解;格物致知,便是以此本知之理为根据而作进一步求知之工夫。常知与真知之不同,如同康德所说的“对道德的一般理性的理解与哲学的理性的理解”之不同,伊川云:
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①
这一段所说的常知与真知,当然是就对道德之了解,而不是泛就一般知识上说。这从“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之语可知。故常知与真知,即普通的理解与深切的理解的不同,是专就对道德的理解的不同层次给出之区别。文中所谓的三尺童子莫不知虎能伤人,是譬喻对于何谓道德的善恶是非,是人所共知的;而以谈虎色变来形容的真知,是指对于本有了解的道德之理,达至真切了解的地步。能真知就自然能“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②
(二)如果程朱通过格物穷理所了解的理是道德之理,而且对此理有正确的了解,则在了解理的过程中,便会回过头来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要按理而行;或严格地讲,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只因为理、义的缘故而给出。此是说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并不同于认知对象般,只给出了对对象的客观的了解,而不必影响行动的主体之态度;在理解道德之理的过程中,由于是就本知之道德之理、应然之理进一步求了解,在不断深化了解中,也就深化了此理对自己行动的主体的要求,即必须要只因为理、义之故而行动。若是则程朱的致知穷理并不如牟先生所说,心与理的关系只是主客的横摄的、认知的关系,即理只能是客而不是主,是所而不是能(“以成其能所之二,认知关系之静摄”③),而应该是在不断深化对于理之知的时候,体证到理是我本有的,是我认可而必须要依之而实践的,这可以说是格物致知之后要反求诸己。理在致知之过程中逐渐成为心要依循的原则,终至心、理为一。程伊川便对格物穷理之后必须“反躬”(《礼记·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即反身以求,回到自己,以实践此理)给出了说明: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①
由此段可证,伊川是认为明理的过程也就是证明“理是我的理”之过程,愈明理,人就愈能反躬而自得。明于外,有证实此理本来是我之理的效果。故伊川亦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程氏遗书》卷18)。言理为我本有,既表示了此理是我本知,又表示了此理是我肯定的。对于道德之理,人一旦理解,便会有以上的感受,因为道德之理是理所当然的,越了解其为当然,便越发会肯定,亦越会产生要依此理以实践的要求。如果可以这样说,则致知以格物穷理,是以自己本有的,对道德之理的常知作根据,作进一步的探究,而达到真知的地步。到了真知理,便可以认为此理为我所有,是我所必须肯定,而且必须实践,有真切的要求;于是这种把理当作对象,以心知来深化、了解的活动,虽然是以横摄的认知性的活动而开始,但最后会以反求诸己,给出按性理而行的,也可以说是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让无条件的为义务而义务的实践具体给出来,那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行的,是我自己自发的要求自己按理而行的,这可以说是纵贯的活动。按理而行,似是横摄的活动,但若此理是我本知,越知而越加肯定,且视为我之理,而且要按理而实践,则亦是自发的,由我决定之行为,而这便是纵贯的。即此时之道德行为,虽然是按理而行,但理是我自己肯定的、自发的去依循的理,不是外在的理,故可说亦是意志之自我立法给出的。亦可说是“性发”,而且是“不容已”的。这是上文伊川所说“反躬”及“物我一理”之说可涵之义。故致知明理而诚意反躬,可以说是从横摄而起纵贯的活动。这种从横起纵的活动,在横摄处说,有主客二分、心理为二的情况,但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活动。一般的认识活动成就的是有关对象的知识,不会因为认知而给出实践的活动,亦不会愈认识而愈证此理为我本有。故可以说这对理之本知、常知,是和依此理而实践相关联的,此对理之知对意志是有要求的,即要求其作去妄存诚之工夫,要主体依理而行,并不能只看作单纯的认知。由于对理有所知,便会有依此理而行动的要求,而若不依此理而行,自己内心一定会感受到不安。如果对于道德法则的认知会有这种效果,则增加明理的程度,就自然会有实践要求的加强。牟先生认定了程朱的心与理为二、以心明理,只能是横摄的认知活动,实践的动力是不能给出来的。如果按上文所说,则牟先生这一论定是可以再商榷的。而人是否可能从对道德法则的清楚了解,而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呢?吾人认为是可以的,这除了上面的论述外,又可以用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互相涵蕴”之论来帮助说明:
这样,“自由”与“一无条件的实践法则”是互相涵蕴的。现在,在这里,我不问:是否它们两者事实上是不同的,抑或是否一个无条件的法则不宁只是一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而此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又是与积极的自由之概念为同一的;我只问:我们的关于“无条件地实践的东西”之知识从何处开始,是否它是从自由开始,抑或是从实践的法则开始?①
这是所谓康德的“交互论”②,由对道德法则的了解与分析,必须肯定人有意志之自由。由对自由的分析,可知自由意志所遵守的法则是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或说自由是道德法则之存在根据,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根据,故曰二者相涵蕴。既然道德法则与自由是“互相涵蕴(互相回溯)”的,则通过对道德法则的深切了解,就会意识到只因为法则的缘故,或被法则直接决定的意志,是人在从事道德的实践时必须要有的。若是则对于道德法则的了解,就会产生纯净化自己意志(力求存心之纯粹)而给出道德行动的要求,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从横起纵”的理论根据,这表示的对道德法则的认识,是从本来有的常知而进至真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要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的要求。这在人的日常心理,也是常见的事实。固然人不一定能给出存心纯粹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要求纯粹依理而行,要求行动的意志纯粹,是人驱之不去的道德的关切。既然有此关切,则对道德行为的加深了解,自然会相应而生起按道德法则而行的自我要求。那么伊川与朱子所主张的,必须以心明理、格物致知的作法为先,固然是横摄,但并非止于对道德之理有认知上的清楚,而必须反躬实践。这种由对于理的真切了解而要求纯粹实践,应该是人常有的感受。如果此说可通,则牟先生对于程朱为横摄系统,陆王为纵贯系统的区分,固然不错,但这两个系统,是可以会通的。从程朱之横摄,可以给出纵贯的道德实践,而陆王肯定心即理,先给出从本心自发的、直贯的道德创造,也必须回过头来,对于此本心或良知中所含的道德之理,作充分的分解以求明白,如此オ可对治道德之存心因感性欲望之反弹而造成之自欺。不然行动的存心如果受感性影响而滑转的话,就容易以情识为良知,而有荡越放肆的流弊。若此说可通,则由程、朱的横摄,固然可以起纵贯;而由陆、王的纵贯,亦须回头作横摄的工夫。这两个系统也可以用《中庸》中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来类比,即明理可以诚身,而诚身也可以有明理的后果,两者是不能偏废的。诚明两进,才可以保证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也可以说是《中庸》的“交互论”。
二、朱子的“明德说”的主旨
上文是据伊川、朱子的从常知到真知之说作了诠解,而这种根据常知进一步达到真知,在真知的情况下会引发真正道德实践的看法,在朱子对《大学》“明德”的说明处可以清楚看到。朱子所理解的明德虽然以理为主,但一定要关联到心知来说,性理在心而为明德。由于心对于理是本有了解的,故此德之“明”也是本有的,故明德之明,不只是说心知之明,而是说心对于理本来就有了解。也可以说心知与理是分不开的,性理在心知中而呈现其明,心知之知本来就有对理的了解在。明德在朱子固然不能理解为本心,不能说明德如同本心良知般,心的活动就是理的呈现;心不同于理或心与理为二,此一区分在朱子是很清楚的。但心虽不同于理,在心知的活动处就有理的彰显,而说性理(性即理也)时,则一定在人的心知中表现其彰明的内容意义。朱子对明德之规定本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其意表达得并不截然清楚。虽不截然,但朱子之语意应该就是如此,以下试引原文来证明此意。朱子的《大学章句》,于“在明明德”句下注曰: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
“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是“要去明了或彰明之”之意,这没有问题。但“明德”究竟是指什么呢?是指心还是性呢?如果指的是性,性是理,性理本身何以可用“明”来形容呢?故如果说性理(道德之理)是光明的,则必须关联到“心知”来说。当然如上文所说,人对道德有特别的关切,所以一旦意识到道德法则就感受到这关于道德法则或道德之理的理解,是很特别的。此时会感受到道德之理是光明昭著而与一般所知的对象是迥然不同的。固然就此义就可以说德性之理是光明的,对于人是彰彰明甚的,但也必须关联到心对于理的了解或认知来说。由于心知的理解、认知才明白到性理的特别意义,体会到道德之理是光明正大的德性。而后文“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则明显是说心,或以心为主来说。因心才能说虚灵,而且才可以具备众理来应对万事。如果是指性理,则用虚灵不昧来形容性理,并不太顺,而且作为明德的性理“具众理而应万事”,更不容易说通。故虚灵不昧以下,应该是说心。但朱子能够直接以心作为明德吗?朱子重视以心知明理的工夫,而并不主张直下相信此心、推扩此心。心要明理才能诚意,才能给出合理的活动。则直接说心是明德,似是肯定心即理,而心便是本体,这应该不合朱子的思想。于是据明德注,对于明德所指究竟是心还是性,就不甚明确。朱子本人是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如云:
或问:“明德便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曰:“便是。”①
按:这一条明确说明德是就仁义礼智等性理来说的,但如上述,性理而曰明德,必须关联到心来说,故另一条《语录》云:
或问:“所谓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言?”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澈,无一毫不明。”②
按:此条对明德之规定最为清楚,亦含“理在心才能说德”之意,此对德之规定甚为重要。说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澈,就表示性理所以能名曰明德,是因为理在心中光明照澈。性理所以会以光明的状态存在于心中,当然与心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如此,亦含此性理是十分特别的,人一知道它,便见其为光明之德性,而认识到其权威性,由于心知之明,性理之特性就光明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表示,心与理虽然不一,但心中有性理照澈,二者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依此意,心知对于性理本有了解之义,就必须肯定。即是说,性理能够说为明德,固然离不开心知的作用,但由于明德是本有的,故心知对于性理的了解,或心知与性理的关联,是有保证的。此可以说性理在心中的光明昭著,与心知对于性理的了解,二者可以说是一事。由于人人都有明德,而且明德未尝息,则据朱子对明德的理解与诠释,心知与性理二者,就必须有关联性,而这种关联不能是经验的、后天的。牟先生由于判定朱子是心与理为二,心性二者平行,心之知理必须是心通过认知的作用而知理,故心的知理是后天的、认知作用的摄取。心与理是后天的、关联的合一。③如果是这样,心的知理与心的合理,就没有保证。而现在如果可以说明心本知理,或性理在心中本来照彻而以明德的情况存在,则心知与德性是有必然的关联性的。如果二者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朱子就不能够说人人都有明德,此是本体之明,而且更不能说虽然昏昧之极,气禀极差或私欲深重的人,都可以有明德的流露(此意见下文)。若这些说法要成立,则心知的知性理,就必须是先验的,即只有心知对于理有先验之知(或说“理性的知识”),才能说人人都有明德。这从朱子区分心理为二,但又肯定性理在心就是明德,而且明德未尝息,就可以推出心对于理一定本有所知之意。于是在朱子,心与理虽然是二,但在心对于理本有所知而为明德的意义下,此二者又不能截然区分,不能说只能以后天的认识,把二者关联在一起,固然心不即是理,但明德使二者相关联,此二者有先验的关联性。此意见下面一条: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德否?”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①
朱子讨论明德的语录不少,上引几段比较有代表性。从这几段看来,明德在朱子是以理为主来说的,但既然是“明”德,需要与心连上关系,故朱子认为明德是理在心中光明照澈,又说此处心性是分不开的,说一个,另外一个就跟着到。可以说心性二者有二而一、一而二的情况。照朱子这些说明,则明德既是性理,而又关联到心来说,虽然明德不是本心,心与理还是有区别的,但心中本来就有性理彰明的存在,心可以根据本具之明德来应万事。如此解说明德,虽然不能像陆王心学的心即理的说法,但可以说心中本有性理的存在,而且对于性理的意义,本来便有了解,不然明德就不好说了。此即表示朱子虽然主张心与理为二,而有心不是理,通过心知可以摄具理之意;但也有虽然心不是理,但心本知理之意。心本知理就有此心之知理是有先验性的之义,心本来就知理,则就可以说人对于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于是成德的工夫,在朱子虽然是要通过心知之明对于理作充分的认识,但这一致知的工夫,是有心对于性理的本知作为根据的。由于是心对于理有本知而为明德,明德是人人都有的,如上文所说,则致知、明理就有先验的、人人本有的对于道德之理的本知作为根据,于是就可以说,朱子这一成德理论是有先验、或超越根据的。当然,既然心与理是二,何以二者可以有先验的关联性,何以心对于理会有本知(或常知)?这是不容易说明的。但人心对于如何判别是非,何谓道德法则,何谓义务,本来就有了解,而且这种对道德的理解是很普遍的,一般人对于何谓道德的行为本有了解,其理解亦正确无误。人都会根据道德之理来要求或判别行动是否有道德性。道德行为的存心是为义而行的,是无条件的行所当行,一般人都据此义作道德判断,即无所为而为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而有条件的、有所为而为,就不算是道德行为,一般人对此道理都很了解,是故康德说可以从一般人的对道德的理性的理解开始,来分析道德法则的涵意。②他认为一般人的这些了解都是可靠的。对于何谓道德行为,何谓道德法则的了解既如此通常,如此普遍,于是吾人可说,朱子虽然不能肯定心与理为一,但肯定心知对于理本有所知,而此对理之知是正确无误,且人皆有之,亦是很有可能,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一般人都有明德作为实践的根据。对于何谓道德,道德价值存在于何处,是在行动的结果,还是行动的存心?人并非没有了解,这应该是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意的根据。以上是我对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总的理解,下文拟从牟先生的有关讨论,再引朱子的有关文献展开论证。
三、论牟先生对朱子“明德说”的诠释与朱子的原意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对明德的规定虽然是性关联着心来说,但应该以性理为主,而且心性二者在朱子有截然的区分,性是心的认知对象,心知的活动是认识的作用,由认识性理而为善,心不是自发自律的给出道德行为的本心的作用,性理为心所知的对象,只是存有之理而没有活动性,于是这种心依理而行的实践,并非由性体不容已而自发给出来的实践活动,而为心通过认知的作用,关联到超越的性理,于是依理而行,性理为心所依的对象,故这种道德的实践,是意志的他律的型态。这是牟先生所理解的朱子的实践理论之型态,于是他认为朱子的“明德注”并未能明白表示此意,应该按照上说的朱子确定之意作修改,需要把心性二者作明白的区分,牟先生的说法如下:
是故依朱子之说统,其在《大学》中关于明德所作之注语实当修改如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可以由虚灵不昧之心知之明以认知地管摄之”之光明正大之性理之谓也。如此修改,不以“虚灵不昧”为首出之主词,省得摇转不定,而亦与朱子之思想一贯。若如原注语,则很易令人误会为承孟子而来之陆王之讲法。①
牟先生这样修改,就确定地把明德规定为“人所得于天的光明正大的性理”,即“明德”只就性理来说。而虚灵不昧专是就心而言,人的心知以其本有的,虚灵不昧的认知能力管摄性理。如此理解明德,则固然清楚区分心性为二,但亦突显心的知理是通过后天的认识而知之义,于是心的知理是没有保证的,人的心知可以知理也可以不知理。经过牟先生这样明确的规定,朱子论明德时,有些意思就似乎被淘汰掉了。如上文所说的,朱子在论明德时心与性是分不开的,“说一个,另一个随到”,依照朱子这些话,心与性在明德处是分不开的。如果二者是分不开的,则可以说是有先验的关联性。另外,明德的作用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此就表示了心统性情之义。心具众理是应万事的根据,故心管摄性理就能够应万事,能应万事是心统性的作用,而应万事的活动就表现了情,故朱子论明德包含了心统性情之义。以此为明德,则心统性情亦是心本有的性能,即心之虚灵本来便可具众理而表现四端来应万事,此心性情三者,在明德中本来是关联在一起的。或可说,由于这三者本来就相关联,于是总起来说明德。如果此说可通,则就不能说心要通过后天的经验认知,才可以关联性理,而表现为四端之情。若依牟先生对“明德注”之修改,心统性情是心之功能,并不能归诸明德。①即不能从明德说心统性情,心的统性情的作用,是通过心知的后天的作用。如此一来,便削弱了以此明德为人人本具的本体之明之义。即心之虚灵的作用是明德本具的,故曰:“心之体用本来如是”,此明是人人原则上有的、本具的妙用,如果这种作用充分发挥,就是心的“全体大用”,所谓心的全体大用,应该是就实现心本来的知理之明,表现心统性情的作用。如果是心通过后天的认知作用而关联到性理,则此妙用及明理之“本来如是”,即本然义,便去掉了。
故牟先生对“明德注”的修改固然很清楚地表达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朱子见解,但以此来解释明德注,则心须通过后天经验的认知作用,才能知理,依理而行,此是后天之渐教,心知理及依理而行,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心之知理是须通过格物穷理以知之,从存在之然之曲折处明善,即从善之事物处明其所以然,这是从“然”以知其“所以然”,这亦不能保证能知道德之理。但牟先生此释于朱子文意,似不甚顺适。因为明德注的原文相当清楚地表示明德是人所得于天,是人人本来便有,而又能虚灵不昧地具众理而应万事,心性二者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牟先生的修改以得于天者是理,虚灵不昧是心,是以心性截然二分的方式来理解明德注。以此一心性二分的格局来说明明德注,虽然很清楚,但不太能表达朱子上文所论明德是“心性相关联,不一不二”之意,亦不能表示明德之“明”未尝息之义。牟先生之修改是见到明德注中似乎以虚灵不昧为主词,但又以性理为实践的客观根据,会产生明德是说心或者是说性的问题,而且如果以明德为心,则心可能就可以往心即理来理解,这不合朱子原意。于是根据他所理解的朱子是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架构,确定的以“性理”为明德,而“虚灵不昧”是心所以能够统摄理的能力,于是明德注就符合心性为二,以心的认知统摄性理而应万事之义,于是就去掉了明德注中原文所含有的心性或心性情本来就先验的相关联之义。牟先生的修改虽然明白,但可能已经把明德注本来含有的一些意思去掉了。
明德以理为主,或甚至直接说是理,如牟先生所说,于朱子文献也有根据,是可以说的。但这明德何以是光明昭著?则必须说此性理是在心中的理,由于在心中,故表现了光明昭著的意义。如上文所说,这里便须有心与理密切的关联在一起而分不开之意。不必如牟先生对朱子注语所作的修正,而明确的规定心性为二,即明德为性理,而由心之认知来关联之,这可以多引一些朱子的原文来说明。在上文已引的明德注中,朱子说:
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
文中明确表示明德之明,是“本体之明”,即其明是人人本具、不会丧失的。于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这明德的流露,而充分实现其明,这即是恢复了明德的本体。如果明德只就性理来说,就不容易表示其是“未尝息”的本体之明之意。因为如果是心理为二,心要通过后天的认知才知道性理,则心对于性理的明白是后天产生的,不能说是本体之明,也不能说是此明未尝息。因此如果要满足此注文之文意,必须肯定性理必可以光明地表现出来,而性理的光明与虚灵不昧的心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此则必须说明德是心与性的连接才可以表现其明,故心的知性,或通过心知而把性理光明地表现出来,就有先验性。此即是说人人都本有这种对于性理的了解,性理在人心中都能光明地表现出来。这应该是朱子的明德注所表达的本意,即心性固然为二,但“心性关连而成”的明德,是有本体的性格的。此本体之明是人人都有的,不会丧失的。《朱子语类》对此有如下的讨论:
此是本领,不可不如此说破。②
此条《大学纂疏》置于“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下。
又曰: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③
按所谓“本领”即是内圣成德的根据,问题是这根据是经验的,还是超越的(先验的)?根据第二条所说“终是遮不得”,可见此明德在日常生活中是随时可以表现出来的,也是人人都可能理解的。故这成德的根据应该是超越的。这才能与“本体之明”之意相应,而若如是,则所谓本领便是成德的超越根据。《语录》又载:
明德未尝息,时时发见于日用之间,如见非义而羞恶,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尊贤而恭敬,见善事而叹慕,皆明德之发见也。如此推之极多。④
朱子如此解“明德未尝息”,是表示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感受到、或认知到性理与道德的意义,这一种对理的知与感受,是人随时都有的。这可以证上文“明德”不能只从性理来说之意。退一步说,若只以理说明德,也可以推出此理发见于日用,而为人心所易知之义。这亦可以证明朱子所说的明德是从人对于道德之理的本知或常知来说,此人对道德之理的知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是可以在生活经验上给出证明的。朱子又说:
人之明德,未尝不明,虽其昏蔽之极,而其善端之发,终不可绝,但当于其所发之端,而接续光明之,则其全体可以常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这里便明将去。①
从“昏蔽之极”的人也有明德之发,可证上文所说的此明是本体之明,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发这种道德的明觉之义。虽然这明德不是心即理的本心,而为心与性理的相关联,但由于是人人都有的本体之明,则心知与理的关联就必须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关联。故心之知性理,可说是先验的知识或“理性的知识”,此知识并非由经验而来。朱子的明德注,有“人之所得乎天”一句,说这是人所得于天的,就表示了这明德是先验的。而如果明德可以从心对于理本有之知来说,则这种知当然也可以说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而由于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则就可以理解何以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是很容易的,一般人都能有的。如上文所说,人一旦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反省,要求自己的行动是道德的行动,那就会很容易看到怎么样的存心给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此意是说,人一旦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要求自己给出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时,他就会以我这行为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做,我这行为的动机或存心是否为人人都该有的动机或存心来反问自己。只要人作出这种道德性的反省,就会按照行为的存心(行动的主观原则)是否为可普遍的,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为道德行为。虽然此意如果要充分展开,或要说明道德法则的全幅内容,并不容易,如康德之分析。但上述的关于何谓道德的理解,人人都有,而且都很恰当,一般人都能够以道德的行为是普遍而必然的,并不出于个人私利之动机来衡量或判断行为是否为道德、是否有道德的意义,这种对道德的本知与常知,是人人都有的经验。是以朱子对明德的了解,如上文所引的文献所说,应该是合理的。人对道德的理解有本知与常知,顺此知而展开之,便可对道德之义作进一步之理解。如“普遍性”与“必然性”是道德法则之特性,不能认为人主观的、偶然的、可容许有例外的作为是道德的行为;又如孟子所说的“义利之辨”,即道德是无条件地为义而行的行为,且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从道德行为只能是为了义所给出的行为,便须肯定义内,即道德法则是人的意志自己给出的。以上对道德的说明,虽然不算详细,但意义已很深切,是一般人都有的道德意识所含的,是很明白的。一般人都用这对道德的认识或其中所含的原理,来鉴别什么是道德行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或道德上的对错是非。这种道德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固然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很清楚,但不表示我们能无例外地或自然地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做,道德行为所要求的无条件性,我们现实上的意志、行动的主体往往不能企及。我们在服膺义务的时候固然知道应该为义务而义务,但是同时我们又会想借着义务的行为得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是康德所说“自然的辩证”之意,这一生命的问题,是从事实践必会遇到、必须加以解决的。因此对于这个道德之理的了解虽然容易,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实践并不容易,但不妨碍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实。我想这应该就是“明德”之所以是“明”之意。就是说德性的道理,人只要稍加反省,要求自己能够遵循“应该”而行动,就可以明白。此明德之明亦可从道德之理十分特别或奇特上说。道德之理是以定然令式来表示的,要人无条件行所当行,它不会用现实上的好处、感性上之满足来吸引人,但就足以令人不得不信服,而且努力去遵守。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特别。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有所为而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考虑、算计再给出行动,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何谓道德行动时,就要把所有考虑、算计抛掉,而无条件的只因为是义的缘故而行,这样的要求行动的存心必须是纯粹的道理或原则,是我们自己认为当该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不得不惭愧、内疚。这一种如此特别的道理非常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心中。因此,虽然明德是要通过我们的心知的理解力,才能清楚地为我们所认识,但我们一旦理解或认识到道德之理时,就会肯定这个道理实在十分清楚、明白,是不容置疑的,于是“明”也必须是道德之理本具的特征,即光明昭著是道德之理本身的特性。德性之理本来就是清楚明白,所以很容易被了解,不同于人通过后天经验而认识到的,有关世界的种种知识道理。我想朱子在界定明德时,一定是考虑到道德之理具备上述的特征,而以此特征来理解明德的“明”之意义。明德是指道德之理,即性理,而由于道德之理有上述清楚、明白,又容易被知的性格,所以可以说明德,又可以说虚灵不昧。虚灵虽然是从心知的作用讲,但不昧是重在性理上说的,即是说对于这种非常清楚明白,人不能不承认的道理,是不能够硬说不明白的,即此理是不容自昧的。对于这个道理你若说不明白,那就是自昧甚至是自欺了。但这一种对于性理的清楚明白,只能是上文所说的常知,而不是真知。必须根据此常知进一步对性理做彻底的了解,才可以说是真知。能真知理就能够诚意。所谓诚意,如同朱子在诚意处的注解:“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①所谓“一于善”是把道德上的善作为自己一心一意的行为目标,也可以说是为了善而为善,没有想到为了其他,而这样才可以说是无自欺,就可以无例外地给出道德行为。此即要自己的心完全合于理。
如果此说可通,则明德是性理在于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在心知中,于是这性理本身清楚明白,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看到这理的彰显。人只要反省一下自己对行动存心的要求,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这理的存在。这样讲明德,就表达了人有一种无论是智或愚都能有的对德性的清楚了解,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固然这个根据不是本心,不能如同陆王之学因为觉悟本心就畅通人的德性根源,而给出道德的行为,但亦有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伊川朱子不能如陆王般直接的承体起用,而必须根据这种本有的、对道德的了解作进一步的了解。要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是需要推致心知的作用,但不能够因为朱子重视后天的以心知知理的作用,就说心与理之二是截然为二,理不是心所本知、本具,而且即使心知理,理也只能是所知的对象,不能反身而成为实践道德的动力。推致心知,亦是推致知中之理,亦可说知与理在致知中同时彰显。故可以说,朱子致知格物的道学问工夫是有先天或先验之根据者。
如此的理解明德,我认为可以说明朱子在明德注中所说“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之意,如果像牟先生所说明德是理,则明德何以不论是智愚都未尝息呢?而且明德是本体之明,即是说人人都有此“明”,而且是不会丧失的。这种本体之明当然必须关联到心知来说,虽然关联到心知,但也必须表示这种心知之明是本有的,此明并不是只就心的认识作用来说,而是就对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即上文所说的常知。人人都有这种对于道德之理一般的了解,一反省就显明出来,谁也不能自昧,于是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明,是就本来就了解理来说的,即“知”不只是理解力或认识能力,而是对理有本来的认识了解。故当朱子说:“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①时,这个知所识的是理,知与理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致知是就心知对于理的本来了解推而致之。虽然“致知在格物”是表示心知要通过对事事物物的穷格,才可以对理有充分的了解,但这是在以心本知理为基础下,通过格物而要求对理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可以这样说,则格物致知的确如朱子《大学章句·格致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此所谓已知之理,是就上文所说的对于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如果可以这样解说,则格物致知是从对于道性理一般的了解进至极致的了解。并不是在不知理的情况下,通过穷格事物之理而取得道德之理的知识。
四、据《大学或问》说明朱子对“明德”的理解
我认为上文对朱子之“明德说”的解释,应可以成立。在朱子的《大学或问》中,有些文字明白表示此意:
“然则此篇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①
据此段朱子所理解的明德,固然重理,但乃是兼理与气,即必须关联到心来说,此处心是主体,由于有心的主宰性的作用,理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他从人得五行之秀,故人有虚灵的心,而在心中万理咸备。固然之所以会以心为贵,是由于心能具理而彰显理,故明德之德,当然重在理,但由于人有灵明的心,故理在心中本来就可以得到彰显,于是这就是如上文所说的成德的超越根据,故致知之知是有对理的本知作为根据,致知就是从已知进至真知。人本来就有对道德之理的本知,这就是人比其他动物可贵的地方。而根据这一对性理的本知,人就可以做到如同圣人般参天地、赞化育。固然参赞是最后才能达到的境界,但成圣的根据,人人本有。据此可知朱子是从人人都有由五行之秀、正通之气构成的可以具众理的心来说人之可贵。如上引文所说“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故朱子所理解的人之所贵,在于人具有本知理的心。有此心,就有此理。他是关联到心知与理两者,即有此心就有性理来说人之可贵,并不是单说心或单说理为人所有来说人之可贵。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确定朱子所说的明德是心、理二者关联在一起,虽然是二者相关联,但必须是先验的及必然的关联在一起的。当然,由于心、理为二,故此本知理而与理关联在一起的心,并不是即是理的实体性的本心,而且心知理的程度,须用工夫来加强。需要对性理(道德之理)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真知,故后文续云:
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成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②
朱子此段反复说明德于人是本有的,一般人或下愚者因为气质的限制、私欲的蒙蔽,使本有的明德不容易彰显;但虽如此,明德还是有表现出来的可能,故曰“明德未尝息”,这就可以证朱子认为即使是下愚者,明德还是可以在其生命中表现出来。朱子所说的明德,虽然不等于陆王所说的心即理的本心,而是在心知中有性理的明白彰显,心与理虽然为二,但这种明德的彰显,虽在下愚也是可能的。此即表达了上文所说的明德作为成德的超越根据之意,也可以证朱子的成德理论或工夫论,是如同程伊川所说的人本有常知,可以根据此常知进到真知的地步。虽然程朱都强调后天的格物致知工夫,但此工夫是有先天本有的对于德性的本知作为根据的。上引文朱子认为不管是何人,即使是昏昧之极者,即下愚之人,在其情绪未发之时,都可以有明德洞然,即明德彰显之时,虽然其彰显可能是非常短的时间。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凡是人都可以有明德彰显之时,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所在。当然这个成德的可能或超越根据,并不能如陆王或孟子所说的本心良知,只要把此心体扩充,充分实现出来就可以,而必须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格物穷理,虽然如此,格物穷理的工夫是有“本体之明”作为根本,并非是全靠后天的认识才能明理。朱子续云:
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此段说明了不论是在大学或是在小学,都是根据本有的明德之明而作教学的工夫。可以说在小学是通过洒扫应对的生活教育来培养明德(“养之于小学之中”的“之”是指明德),在大学则是通过格物致知来使明德进一步彰显,乃至于使心知充分明理,而恢复理的全体的意义,对于理的表里精粗都能了解,也就是心知的全体大用充分明朗。这虽然是从心知与理两方面说,但二者也是关联在一起,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朱子的小学与大学的教学工夫,都是有本有的明德作为根据,通过大学的格物致知的工夫,就可以恢复心的全体,这所谓全体,就是心知对于本知的性理得到完全的了解,这也就同于伊川从常知到真知的程序。而且即使到此地步,也是人人本有的明德之发挥,并非在性分之外,另作增加的、没有本源之事。朱子续云:
向也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①
这是通过自明其明德而新民,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本于原有的明德而自己用工夫,加以进一步彰显,虽然做到充分明明德的地步,也不是对于人人本有的明德有所增加,由此也可见,朱子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而使心知理达到充分明白的地步,只是恢复明德的本体之明,并不是有所增加,这表示心知对于理的充分明白,只是对本来有的做加强的工夫,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本来没有的认识。这一方面肯定对于理本来有所了解的明德人人都有,而且会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主张必须进一步求知,到对于理有真知,才能持久地维持道德的实践,这是朱子强调道问学之意,但不能因为强调道问学,就说朱子不肯定人对道德之理本有所知,以致其格物致知是求理于外的“义外”之论。从以上《大学或问》的说法,可证朱子并非如牟先生所说的,是“后天渐教”的义理型态,由于对明德本有,而且未尝作出肯定,则朱子这一渐教的系统有先天的根据。故朱子的格物致知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通过心知对理的真切了解而恢复本有的明德之全体大用,在人人本有的明德此一意义上说,人的心知本来具理,而性理本来也有其光明的作用。由于心性二而不二,可以这样相互补充地来说。
在《大学或问》论知的一段,很能表达“知”的特殊性: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欲勉强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②
此段说“知”是心之神明,此一说法,比“心者,人之神明”③更进了一步。心是人之神明,而知则是心之神明,表示了“知”是心的最本质的作用。此一表示可以了解明德注所说的“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固然是说心的作用,但可以更确定地说,这是知的妙用。知的作用是所谓“妙众理”,说“妙众理”是比“具众理”更进一步的,这是表达了“知”把理的意义、作用具体表现出来之意。在《大学纂疏》引的《语录》曰:“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第13页)以虚灵来规定心之本体,就表示了此虚灵是知,而知是心之神明之意。据此,此知并不能理解为心、理为二的心之认知作用,而是此知之虚灵,与性理是相关联的,也可以说知中有理,能充分发挥此知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虚灵不昧的作用),则知中的理,就可以彰显出来。由此可证,朱子所说致知,不止是致心之认知作用,而是知与理都在其中。又在“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处,引语录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第32页)此段很能说明上述之意。理是自己本有的,故知理并非知一外在对象,而是将在我之理发出来。如果不是知中含理,或如上文所说,知与理有先验的关联性,是不能如此说的。
以上论明德,认为当以心关联性理而言,而此关联有先验性;实践的客观根据是理,然而心知对于理本有所知,吾人以为这是朱子言明德之本意,但朱子的有关言论,确有使人从心说明德或从性说明德两种解读的可能,由此也可以理解何以朱子之后会有明德如何理解、如何规定的论争,朱子对明德的规定,确有模棱两可处。朝鲜朝的学者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认为朱子对于心的看法可以分为“以理言”与“以气言”,而以理言之心就是明德,明德注中所说的虚灵固然是心,但这是以理言之心,故明德须以理来规定,这是所谓“明德是理”之说。虽然他说明德是理,但其实是关联到心来说的理,也表示了理在心中有其作用,故可以说明德。他将朱子明德注中所涉及的心性情三者都说是理。他这一说法在他的弟子中,引发了争论。柳重教(号省斋,1821—1893)对师说作了修正,认为心的“正说”应该还是从气来规定。他的同门金平默(号重庵,1819—1891),与他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他们俩人的门人继续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是朝鲜朝儒学史上后期的一个重要论争。①当时另一名儒田愚(号艮斋,1841—1922)对华西“明德是理”之说大加反对,主张“明德是心”。艮斋对明德之规定,大体同于牟宗三先生之说。这场朝鲜朝之论争与本文所论,可以有对照之作用,但其中论辩颇多曲折,须另作专文来讨论。
五、结论
朱子对明德的理解,由于关联到性理与心知,其意义的确不很清楚,故牟宗三先生严格区分心、理为二,明德只能从性理说,而心知对于理的了解,是通过后天的经验,以认知的作用,使心涵摄理,而这种解释虽然清楚,也符合朱子心、理为二的规定,但心认知地摄取理,是后天的作用,如是,则心的知理是后天的认知,便没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人心的知理就不能够有保证。于是牟先生把朱子的义理形态判为横摄系统,而且是后天的渐教。这种以后天的认识来使心摄具理的形态,虽然强调了心知的经验认知作用,与后天的学习之重要,但没有能够给出心知知理的保证,也不能给出心之明理之后,能够依理而行的实践的动力。如果对朱子成德的理论作这样的衡定,则朱子之学当然是有理论上不足的地方。但据上文吾人所作的有关朱子的明德注的分析,似乎可以证明,明德虽然有心、理二者相关联来理解之意,但心知与性理二者的关联是先验性的关联,
即性理本来在心中就可以明白地昭显出来,而且心知对于性理之知是本有的。由于性理在心中的昭显,即明德,是人人都有的,虽气质昏昧或私欲深重的人,其明德都未尝息,则人可以根据这本有的明德,来进一步格物致知,即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致乎其极”,则此格物致知的工夫,是有本有的明德,即对于理之本知作根据的。故不能是后天的渐教,而是具有先天根据的渐教。如是,则朱子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并非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说法,也不必说是“异质的跳跃”。由于致知是从本有的、对仁义礼智的常知开始,则充分了解而真知性理,当然是可能的,而在格致的过程中,朱子强调此理是我的理,并非从外入,而且在知理时,也会要求自己非要遵照此理而行不可,这种说法及肯定,也是说得通的。于是格物致知以求对理有真知,在真知理时就可以诚意,即要求自己完全按理而行,这也是可能的情况,说明其并不困难。
当然如此说明德与理解朱子的理论形态,并不能与陆王肯定心即理的形态相混,陆王学从本心良知之呈现,体证到此便是天理所在,把此良知本体充分实现,就可以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一工夫进路,当然是简截有力,可以当下给出道德行动或实践的根源及其动力。而伊川朱子根据人对道德的本知、常知,而进一步致知以求对理有真知,这虽然不是当下把不容已的、自发为善的本心体现、扩充出来,但由于所知的是道德的性理,在有本知作根据的情况下,不会造成因为格物穷理而对道德之理作歧出的了解。而且之所以要从本知的道德之理说到太极之理、天理,是要追问道德之理的根源来处,从然追问其所以然。如果“然”是道德之理,而且是在日用中到处表现的明德,如孝悌慈与忠信等,则根据这些理来作所以然的推证,不应该会歧出。不单只不歧出,而且可以因为这种形而上的推证,明白道德之理的根源来处,说明其为存在之理,而增强了人必须依理而行的说服力。故伊川朱子学虽然不是承本心的不容已而起用的工夫,而是通过对于理的了解的加强,来使行动的意志逐渐纯化的作法,但此一作法或工夫,应该也是可以与陆王学并立,而为成德之教另一有效的工夫理论。而且程朱这一进路,对于人的成德而遭遇到的生命上的问题,有不可取代的克治的作用。因为人在要求自己以道德义务作为行动的唯一依据或原则时,人的感性欲求会起来相争,力图要求人在纯粹的践德时,也要照顾感性欲求的需要,于是很容易的,会将无条件实践的存心转成为有条件的,这是上文一再提到之康德所谓的“自然的辩证”,此即人之“根本恶”①,由于有这自然辩证的现象存在,所以康德认为人必须在对道德法则有所了解的情况,进一步对道德之理作哲学的分析,即所谓从一般的对道德的理性的理解,进至哲学的理解。康德说明对于道德之理的从一般的理解到哲学的理解,是成德必须具有的工夫,即道德实践必须求助于学问或哲学。康德此一说法正好帮助我们理解伊川朱子何以不直接从人对道德法则本有了解处,作充分的力图实践的工夫,而要先从事对本知的道德之理作充分的了解。如果此说可通,则伊川与朱子之所以走这种格物致知的道路,认为先致知才能诚意,也有在实践上不得不如此的缘故。
参考文献:
1.[宋]赵顺孙撰,黄坤整理:《大学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2年。
2.[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四部备要》本),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
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宋]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李恒老:《华西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04册,2003年。
7.柳重教:《省斋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23-324册,2004年。
8.田愚:《艮斋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33册,2003年。
9.[美]H.E.Allison,Kant’s Theory ofFree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韩]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
1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
12.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13.亨利·E.阿利森著,陈虎平译:《康德的自由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康德:《道德形上学基本原理》,牟宗三译注《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5.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牟宗三译注《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6.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重要论争续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
17.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8.杨祖汉:《程伊川、朱子“真知”说新诠——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观点看》,《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2期,总第16期(2011年12月),第177~203页。
19.杨祖汉:《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当代儒学研究》第24期(2018年6月),第47~68页。
一、伊川、朱子可能是从横起纵的实践理论型态
朱子对《大学》十分看重,认为在他一生中,看得最明白的文章就是《大学》①。他借《大学》的三纲八目的内容,给出了儒学成德之教的工夫程序,固然这一设计与铺陈是根据《大学》文本,及承继了程伊川的讲法,但朱子的发明很多。他对《大学》的诠释及有关讨论,纲举目张,很清楚地表达实践成德的工夫与程序,及其根据。朱子此解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可说是南宋以后普遍成为士人作修养工夫的标准教法。虽然对于朱子学的诠释,近世由于牟宗三先生“别子为宗”的衡定,使朱子的思想理论比较不像过去,虽有朱陆异同,及王学盛行,仍无异议地被视为儒学的正宗。但牟先生的朱子诠释也很明显与过去八百年中国乃至于东亚社会尊崇朱子的事实有距离,于是,对于牟先生的诠释,当代是不断有商榷的意见提出的,只是大多数的反对意见不能有严格的哲学论证与对朱子文献的明白诠释作根据,对牟先生的说法于是便不能有所撼动。我近年对此作了一些思考,借着与康德之道德哲学比较,对伊川、朱子的理论型态作了一些新诠。康德肯定通常的理性(一般人)对道德法则有正确的了解,但必须从对法则的一般了解进到哲学的了解,才可以挡住人随顺感性之欲求,对要求人无条件地践德之道德意识给出挑战,而生起的“自然的辩证”②;此意正好可以说明伊川、朱子致知以求真知之义,即说明此主张的用心及其必要性。康德认为对付这自然的辩证,避免人道德的堕落,必须将道德法则从一般经验中抽出来,而明其为先验普遍之理。这一分析,即说明道德法则是根于纯粹理性的。此一康德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或对道德之根本原理的说明,亦如同伊川、朱子对性理之分解,即严格区分心性、理气有形上形下之异之作法。由此可见,程朱的格物穷理,是从人本来便有的对道德之理之了解(本知、常知),进至对道德之理有真知、切感的地步,故由格致可以达致诚意的结果。由是我认为程朱之义理型态并非如牟先生所说为儒门别子,而是可以与陆王并立,同为儒学应有,或甚至必须有的一个成德理论。二系虽有主理及主心的不同,但亦可以会通。③
如果上说可通,则对于牟先生的朱子诠释,我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一)朱子虽然清楚区分心、理为二,但并非表示心对于理本无所知,而要通过格物,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然出发追问其所以然的方式,才能了解性理。依朱子可以是认为人对于理本有所知,只是必需从一般的了解进到真知,于是将本知之理抽出来作进一步的理解;格物致知,便是以此本知之理为根据而作进一步求知之工夫。常知与真知之不同,如同康德所说的“对道德的一般理性的理解与哲学的理性的理解”之不同,伊川云:
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①
这一段所说的常知与真知,当然是就对道德之了解,而不是泛就一般知识上说。这从“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之语可知。故常知与真知,即普通的理解与深切的理解的不同,是专就对道德的理解的不同层次给出之区别。文中所谓的三尺童子莫不知虎能伤人,是譬喻对于何谓道德的善恶是非,是人所共知的;而以谈虎色变来形容的真知,是指对于本有了解的道德之理,达至真切了解的地步。能真知就自然能“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②
(二)如果程朱通过格物穷理所了解的理是道德之理,而且对此理有正确的了解,则在了解理的过程中,便会回过头来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要按理而行;或严格地讲,要求自己行动的意志只因为理、义的缘故而给出。此是说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并不同于认知对象般,只给出了对对象的客观的了解,而不必影响行动的主体之态度;在理解道德之理的过程中,由于是就本知之道德之理、应然之理进一步求了解,在不断深化了解中,也就深化了此理对自己行动的主体的要求,即必须要只因为理、义之故而行动。若是则程朱的致知穷理并不如牟先生所说,心与理的关系只是主客的横摄的、认知的关系,即理只能是客而不是主,是所而不是能(“以成其能所之二,认知关系之静摄”③),而应该是在不断深化对于理之知的时候,体证到理是我本有的,是我认可而必须要依之而实践的,这可以说是格物致知之后要反求诸己。理在致知之过程中逐渐成为心要依循的原则,终至心、理为一。程伊川便对格物穷理之后必须“反躬”(《礼记·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即反身以求,回到自己,以实践此理)给出了说明: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①
由此段可证,伊川是认为明理的过程也就是证明“理是我的理”之过程,愈明理,人就愈能反躬而自得。明于外,有证实此理本来是我之理的效果。故伊川亦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程氏遗书》卷18)。言理为我本有,既表示了此理是我本知,又表示了此理是我肯定的。对于道德之理,人一旦理解,便会有以上的感受,因为道德之理是理所当然的,越了解其为当然,便越发会肯定,亦越会产生要依此理以实践的要求。如果可以这样说,则致知以格物穷理,是以自己本有的,对道德之理的常知作根据,作进一步的探究,而达到真知的地步。到了真知理,便可以认为此理为我所有,是我所必须肯定,而且必须实践,有真切的要求;于是这种把理当作对象,以心知来深化、了解的活动,虽然是以横摄的认知性的活动而开始,但最后会以反求诸己,给出按性理而行的,也可以说是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让无条件的为义务而义务的实践具体给出来,那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行的,是我自己自发的要求自己按理而行的,这可以说是纵贯的活动。按理而行,似是横摄的活动,但若此理是我本知,越知而越加肯定,且视为我之理,而且要按理而实践,则亦是自发的,由我决定之行为,而这便是纵贯的。即此时之道德行为,虽然是按理而行,但理是我自己肯定的、自发的去依循的理,不是外在的理,故可说亦是意志之自我立法给出的。亦可说是“性发”,而且是“不容已”的。这是上文伊川所说“反躬”及“物我一理”之说可涵之义。故致知明理而诚意反躬,可以说是从横摄而起纵贯的活动。这种从横起纵的活动,在横摄处说,有主客二分、心理为二的情况,但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活动。一般的认识活动成就的是有关对象的知识,不会因为认知而给出实践的活动,亦不会愈认识而愈证此理为我本有。故可以说这对理之本知、常知,是和依此理而实践相关联的,此对理之知对意志是有要求的,即要求其作去妄存诚之工夫,要主体依理而行,并不能只看作单纯的认知。由于对理有所知,便会有依此理而行动的要求,而若不依此理而行,自己内心一定会感受到不安。如果对于道德法则的认知会有这种效果,则增加明理的程度,就自然会有实践要求的加强。牟先生认定了程朱的心与理为二、以心明理,只能是横摄的认知活动,实践的动力是不能给出来的。如果按上文所说,则牟先生这一论定是可以再商榷的。而人是否可能从对道德法则的清楚了解,而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呢?吾人认为是可以的,这除了上面的论述外,又可以用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互相涵蕴”之论来帮助说明:
这样,“自由”与“一无条件的实践法则”是互相涵蕴的。现在,在这里,我不问:是否它们两者事实上是不同的,抑或是否一个无条件的法则不宁只是一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而此纯粹实践理性之意识又是与积极的自由之概念为同一的;我只问:我们的关于“无条件地实践的东西”之知识从何处开始,是否它是从自由开始,抑或是从实践的法则开始?①
这是所谓康德的“交互论”②,由对道德法则的了解与分析,必须肯定人有意志之自由。由对自由的分析,可知自由意志所遵守的法则是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或说自由是道德法则之存在根据,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根据,故曰二者相涵蕴。既然道德法则与自由是“互相涵蕴(互相回溯)”的,则通过对道德法则的深切了解,就会意识到只因为法则的缘故,或被法则直接决定的意志,是人在从事道德的实践时必须要有的。若是则对于道德法则的了解,就会产生纯净化自己意志(力求存心之纯粹)而给出道德行动的要求,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从横起纵”的理论根据,这表示的对道德法则的认识,是从本来有的常知而进至真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要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的要求。这在人的日常心理,也是常见的事实。固然人不一定能给出存心纯粹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要求纯粹依理而行,要求行动的意志纯粹,是人驱之不去的道德的关切。既然有此关切,则对道德行为的加深了解,自然会相应而生起按道德法则而行的自我要求。那么伊川与朱子所主张的,必须以心明理、格物致知的作法为先,固然是横摄,但并非止于对道德之理有认知上的清楚,而必须反躬实践。这种由对于理的真切了解而要求纯粹实践,应该是人常有的感受。如果此说可通,则牟先生对于程朱为横摄系统,陆王为纵贯系统的区分,固然不错,但这两个系统,是可以会通的。从程朱之横摄,可以给出纵贯的道德实践,而陆王肯定心即理,先给出从本心自发的、直贯的道德创造,也必须回过头来,对于此本心或良知中所含的道德之理,作充分的分解以求明白,如此オ可对治道德之存心因感性欲望之反弹而造成之自欺。不然行动的存心如果受感性影响而滑转的话,就容易以情识为良知,而有荡越放肆的流弊。若此说可通,则由程、朱的横摄,固然可以起纵贯;而由陆、王的纵贯,亦须回头作横摄的工夫。这两个系统也可以用《中庸》中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来类比,即明理可以诚身,而诚身也可以有明理的后果,两者是不能偏废的。诚明两进,才可以保证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也可以说是《中庸》的“交互论”。
二、朱子的“明德说”的主旨
上文是据伊川、朱子的从常知到真知之说作了诠解,而这种根据常知进一步达到真知,在真知的情况下会引发真正道德实践的看法,在朱子对《大学》“明德”的说明处可以清楚看到。朱子所理解的明德虽然以理为主,但一定要关联到心知来说,性理在心而为明德。由于心对于理是本有了解的,故此德之“明”也是本有的,故明德之明,不只是说心知之明,而是说心对于理本来就有了解。也可以说心知与理是分不开的,性理在心知中而呈现其明,心知之知本来就有对理的了解在。明德在朱子固然不能理解为本心,不能说明德如同本心良知般,心的活动就是理的呈现;心不同于理或心与理为二,此一区分在朱子是很清楚的。但心虽不同于理,在心知的活动处就有理的彰显,而说性理(性即理也)时,则一定在人的心知中表现其彰明的内容意义。朱子对明德之规定本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其意表达得并不截然清楚。虽不截然,但朱子之语意应该就是如此,以下试引原文来证明此意。朱子的《大学章句》,于“在明明德”句下注曰: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
“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是“要去明了或彰明之”之意,这没有问题。但“明德”究竟是指什么呢?是指心还是性呢?如果指的是性,性是理,性理本身何以可用“明”来形容呢?故如果说性理(道德之理)是光明的,则必须关联到“心知”来说。当然如上文所说,人对道德有特别的关切,所以一旦意识到道德法则就感受到这关于道德法则或道德之理的理解,是很特别的。此时会感受到道德之理是光明昭著而与一般所知的对象是迥然不同的。固然就此义就可以说德性之理是光明的,对于人是彰彰明甚的,但也必须关联到心对于理的了解或认知来说。由于心知的理解、认知才明白到性理的特别意义,体会到道德之理是光明正大的德性。而后文“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则明显是说心,或以心为主来说。因心才能说虚灵,而且才可以具备众理来应对万事。如果是指性理,则用虚灵不昧来形容性理,并不太顺,而且作为明德的性理“具众理而应万事”,更不容易说通。故虚灵不昧以下,应该是说心。但朱子能够直接以心作为明德吗?朱子重视以心知明理的工夫,而并不主张直下相信此心、推扩此心。心要明理才能诚意,才能给出合理的活动。则直接说心是明德,似是肯定心即理,而心便是本体,这应该不合朱子的思想。于是据明德注,对于明德所指究竟是心还是性,就不甚明确。朱子本人是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如云:
或问:“明德便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曰:“便是。”①
按:这一条明确说明德是就仁义礼智等性理来说的,但如上述,性理而曰明德,必须关联到心来说,故另一条《语录》云:
或问:“所谓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言?”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澈,无一毫不明。”②
按:此条对明德之规定最为清楚,亦含“理在心才能说德”之意,此对德之规定甚为重要。说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澈,就表示性理所以能名曰明德,是因为理在心中光明照澈。性理所以会以光明的状态存在于心中,当然与心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如此,亦含此性理是十分特别的,人一知道它,便见其为光明之德性,而认识到其权威性,由于心知之明,性理之特性就光明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表示,心与理虽然不一,但心中有性理照澈,二者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依此意,心知对于性理本有了解之义,就必须肯定。即是说,性理能够说为明德,固然离不开心知的作用,但由于明德是本有的,故心知对于性理的了解,或心知与性理的关联,是有保证的。此可以说性理在心中的光明昭著,与心知对于性理的了解,二者可以说是一事。由于人人都有明德,而且明德未尝息,则据朱子对明德的理解与诠释,心知与性理二者,就必须有关联性,而这种关联不能是经验的、后天的。牟先生由于判定朱子是心与理为二,心性二者平行,心之知理必须是心通过认知的作用而知理,故心的知理是后天的、认知作用的摄取。心与理是后天的、关联的合一。③如果是这样,心的知理与心的合理,就没有保证。而现在如果可以说明心本知理,或性理在心中本来照彻而以明德的情况存在,则心知与德性是有必然的关联性的。如果二者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朱子就不能够说人人都有明德,此是本体之明,而且更不能说虽然昏昧之极,气禀极差或私欲深重的人,都可以有明德的流露(此意见下文)。若这些说法要成立,则心知的知性理,就必须是先验的,即只有心知对于理有先验之知(或说“理性的知识”),才能说人人都有明德。这从朱子区分心理为二,但又肯定性理在心就是明德,而且明德未尝息,就可以推出心对于理一定本有所知之意。于是在朱子,心与理虽然是二,但在心对于理本有所知而为明德的意义下,此二者又不能截然区分,不能说只能以后天的认识,把二者关联在一起,固然心不即是理,但明德使二者相关联,此二者有先验的关联性。此意见下面一条: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德否?”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①
朱子讨论明德的语录不少,上引几段比较有代表性。从这几段看来,明德在朱子是以理为主来说的,但既然是“明”德,需要与心连上关系,故朱子认为明德是理在心中光明照澈,又说此处心性是分不开的,说一个,另外一个就跟着到。可以说心性二者有二而一、一而二的情况。照朱子这些说明,则明德既是性理,而又关联到心来说,虽然明德不是本心,心与理还是有区别的,但心中本来就有性理彰明的存在,心可以根据本具之明德来应万事。如此解说明德,虽然不能像陆王心学的心即理的说法,但可以说心中本有性理的存在,而且对于性理的意义,本来便有了解,不然明德就不好说了。此即表示朱子虽然主张心与理为二,而有心不是理,通过心知可以摄具理之意;但也有虽然心不是理,但心本知理之意。心本知理就有此心之知理是有先验性的之义,心本来就知理,则就可以说人对于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于是成德的工夫,在朱子虽然是要通过心知之明对于理作充分的认识,但这一致知的工夫,是有心对于性理的本知作为根据的。由于是心对于理有本知而为明德,明德是人人都有的,如上文所说,则致知、明理就有先验的、人人本有的对于道德之理的本知作为根据,于是就可以说,朱子这一成德理论是有先验、或超越根据的。当然,既然心与理是二,何以二者可以有先验的关联性,何以心对于理会有本知(或常知)?这是不容易说明的。但人心对于如何判别是非,何谓道德法则,何谓义务,本来就有了解,而且这种对道德的理解是很普遍的,一般人对于何谓道德的行为本有了解,其理解亦正确无误。人都会根据道德之理来要求或判别行动是否有道德性。道德行为的存心是为义而行的,是无条件的行所当行,一般人都据此义作道德判断,即无所为而为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而有条件的、有所为而为,就不算是道德行为,一般人对此道理都很了解,是故康德说可以从一般人的对道德的理性的理解开始,来分析道德法则的涵意。②他认为一般人的这些了解都是可靠的。对于何谓道德行为,何谓道德法则的了解既如此通常,如此普遍,于是吾人可说,朱子虽然不能肯定心与理为一,但肯定心知对于理本有所知,而此对理之知是正确无误,且人皆有之,亦是很有可能,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一般人都有明德作为实践的根据。对于何谓道德,道德价值存在于何处,是在行动的结果,还是行动的存心?人并非没有了解,这应该是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意的根据。以上是我对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总的理解,下文拟从牟先生的有关讨论,再引朱子的有关文献展开论证。
三、论牟先生对朱子“明德说”的诠释与朱子的原意
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对明德的规定虽然是性关联着心来说,但应该以性理为主,而且心性二者在朱子有截然的区分,性是心的认知对象,心知的活动是认识的作用,由认识性理而为善,心不是自发自律的给出道德行为的本心的作用,性理为心所知的对象,只是存有之理而没有活动性,于是这种心依理而行的实践,并非由性体不容已而自发给出来的实践活动,而为心通过认知的作用,关联到超越的性理,于是依理而行,性理为心所依的对象,故这种道德的实践,是意志的他律的型态。这是牟先生所理解的朱子的实践理论之型态,于是他认为朱子的“明德注”并未能明白表示此意,应该按照上说的朱子确定之意作修改,需要把心性二者作明白的区分,牟先生的说法如下:
是故依朱子之说统,其在《大学》中关于明德所作之注语实当修改如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可以由虚灵不昧之心知之明以认知地管摄之”之光明正大之性理之谓也。如此修改,不以“虚灵不昧”为首出之主词,省得摇转不定,而亦与朱子之思想一贯。若如原注语,则很易令人误会为承孟子而来之陆王之讲法。①
牟先生这样修改,就确定地把明德规定为“人所得于天的光明正大的性理”,即“明德”只就性理来说。而虚灵不昧专是就心而言,人的心知以其本有的,虚灵不昧的认知能力管摄性理。如此理解明德,则固然清楚区分心性为二,但亦突显心的知理是通过后天的认识而知之义,于是心的知理是没有保证的,人的心知可以知理也可以不知理。经过牟先生这样明确的规定,朱子论明德时,有些意思就似乎被淘汰掉了。如上文所说的,朱子在论明德时心与性是分不开的,“说一个,另一个随到”,依照朱子这些话,心与性在明德处是分不开的。如果二者是分不开的,则可以说是有先验的关联性。另外,明德的作用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此就表示了心统性情之义。心具众理是应万事的根据,故心管摄性理就能够应万事,能应万事是心统性的作用,而应万事的活动就表现了情,故朱子论明德包含了心统性情之义。以此为明德,则心统性情亦是心本有的性能,即心之虚灵本来便可具众理而表现四端来应万事,此心性情三者,在明德中本来是关联在一起的。或可说,由于这三者本来就相关联,于是总起来说明德。如果此说可通,则就不能说心要通过后天的经验认知,才可以关联性理,而表现为四端之情。若依牟先生对“明德注”之修改,心统性情是心之功能,并不能归诸明德。①即不能从明德说心统性情,心的统性情的作用,是通过心知的后天的作用。如此一来,便削弱了以此明德为人人本具的本体之明之义。即心之虚灵的作用是明德本具的,故曰:“心之体用本来如是”,此明是人人原则上有的、本具的妙用,如果这种作用充分发挥,就是心的“全体大用”,所谓心的全体大用,应该是就实现心本来的知理之明,表现心统性情的作用。如果是心通过后天的认知作用而关联到性理,则此妙用及明理之“本来如是”,即本然义,便去掉了。
故牟先生对“明德注”的修改固然很清楚地表达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朱子见解,但以此来解释明德注,则心须通过后天经验的认知作用,才能知理,依理而行,此是后天之渐教,心知理及依理而行,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心之知理是须通过格物穷理以知之,从存在之然之曲折处明善,即从善之事物处明其所以然,这是从“然”以知其“所以然”,这亦不能保证能知道德之理。但牟先生此释于朱子文意,似不甚顺适。因为明德注的原文相当清楚地表示明德是人所得于天,是人人本来便有,而又能虚灵不昧地具众理而应万事,心性二者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牟先生的修改以得于天者是理,虚灵不昧是心,是以心性截然二分的方式来理解明德注。以此一心性二分的格局来说明明德注,虽然很清楚,但不太能表达朱子上文所论明德是“心性相关联,不一不二”之意,亦不能表示明德之“明”未尝息之义。牟先生之修改是见到明德注中似乎以虚灵不昧为主词,但又以性理为实践的客观根据,会产生明德是说心或者是说性的问题,而且如果以明德为心,则心可能就可以往心即理来理解,这不合朱子原意。于是根据他所理解的朱子是心性二分、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架构,确定的以“性理”为明德,而“虚灵不昧”是心所以能够统摄理的能力,于是明德注就符合心性为二,以心的认知统摄性理而应万事之义,于是就去掉了明德注中原文所含有的心性或心性情本来就先验的相关联之义。牟先生的修改虽然明白,但可能已经把明德注本来含有的一些意思去掉了。
明德以理为主,或甚至直接说是理,如牟先生所说,于朱子文献也有根据,是可以说的。但这明德何以是光明昭著?则必须说此性理是在心中的理,由于在心中,故表现了光明昭著的意义。如上文所说,这里便须有心与理密切的关联在一起而分不开之意。不必如牟先生对朱子注语所作的修正,而明确的规定心性为二,即明德为性理,而由心之认知来关联之,这可以多引一些朱子的原文来说明。在上文已引的明德注中,朱子说:
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
文中明确表示明德之明,是“本体之明”,即其明是人人本具、不会丧失的。于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这明德的流露,而充分实现其明,这即是恢复了明德的本体。如果明德只就性理来说,就不容易表示其是“未尝息”的本体之明之意。因为如果是心理为二,心要通过后天的认知才知道性理,则心对于性理的明白是后天产生的,不能说是本体之明,也不能说是此明未尝息。因此如果要满足此注文之文意,必须肯定性理必可以光明地表现出来,而性理的光明与虚灵不昧的心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此则必须说明德是心与性的连接才可以表现其明,故心的知性,或通过心知而把性理光明地表现出来,就有先验性。此即是说人人都本有这种对于性理的了解,性理在人心中都能光明地表现出来。这应该是朱子的明德注所表达的本意,即心性固然为二,但“心性关连而成”的明德,是有本体的性格的。此本体之明是人人都有的,不会丧失的。《朱子语类》对此有如下的讨论:
此是本领,不可不如此说破。②
此条《大学纂疏》置于“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下。
又曰: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③
按所谓“本领”即是内圣成德的根据,问题是这根据是经验的,还是超越的(先验的)?根据第二条所说“终是遮不得”,可见此明德在日常生活中是随时可以表现出来的,也是人人都可能理解的。故这成德的根据应该是超越的。这才能与“本体之明”之意相应,而若如是,则所谓本领便是成德的超越根据。《语录》又载:
明德未尝息,时时发见于日用之间,如见非义而羞恶,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尊贤而恭敬,见善事而叹慕,皆明德之发见也。如此推之极多。④
朱子如此解“明德未尝息”,是表示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感受到、或认知到性理与道德的意义,这一种对理的知与感受,是人随时都有的。这可以证上文“明德”不能只从性理来说之意。退一步说,若只以理说明德,也可以推出此理发见于日用,而为人心所易知之义。这亦可以证明朱子所说的明德是从人对于道德之理的本知或常知来说,此人对道德之理的知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是可以在生活经验上给出证明的。朱子又说:
人之明德,未尝不明,虽其昏蔽之极,而其善端之发,终不可绝,但当于其所发之端,而接续光明之,则其全体可以常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这里便明将去。①
从“昏蔽之极”的人也有明德之发,可证上文所说的此明是本体之明,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发这种道德的明觉之义。虽然这明德不是心即理的本心,而为心与性理的相关联,但由于是人人都有的本体之明,则心知与理的关联就必须是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关联。故心之知性理,可说是先验的知识或“理性的知识”,此知识并非由经验而来。朱子的明德注,有“人之所得乎天”一句,说这是人所得于天的,就表示了这明德是先验的。而如果明德可以从心对于理本有之知来说,则这种知当然也可以说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而由于是先验的、理性的知识,则就可以理解何以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是很容易的,一般人都能有的。如上文所说,人一旦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反省,要求自己的行动是道德的行动,那就会很容易看到怎么样的存心给出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此意是说,人一旦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要求自己给出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时,他就会以我这行为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做,我这行为的动机或存心是否为人人都该有的动机或存心来反问自己。只要人作出这种道德性的反省,就会按照行为的存心(行动的主观原则)是否为可普遍的,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为道德行为。虽然此意如果要充分展开,或要说明道德法则的全幅内容,并不容易,如康德之分析。但上述的关于何谓道德的理解,人人都有,而且都很恰当,一般人都能够以道德的行为是普遍而必然的,并不出于个人私利之动机来衡量或判断行为是否为道德、是否有道德的意义,这种对道德的本知与常知,是人人都有的经验。是以朱子对明德的了解,如上文所引的文献所说,应该是合理的。人对道德的理解有本知与常知,顺此知而展开之,便可对道德之义作进一步之理解。如“普遍性”与“必然性”是道德法则之特性,不能认为人主观的、偶然的、可容许有例外的作为是道德的行为;又如孟子所说的“义利之辨”,即道德是无条件地为义而行的行为,且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从道德行为只能是为了义所给出的行为,便须肯定义内,即道德法则是人的意志自己给出的。以上对道德的说明,虽然不算详细,但意义已很深切,是一般人都有的道德意识所含的,是很明白的。一般人都用这对道德的认识或其中所含的原理,来鉴别什么是道德行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或道德上的对错是非。这种道德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固然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很清楚,但不表示我们能无例外地或自然地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做,道德行为所要求的无条件性,我们现实上的意志、行动的主体往往不能企及。我们在服膺义务的时候固然知道应该为义务而义务,但是同时我们又会想借着义务的行为得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是康德所说“自然的辩证”之意,这一生命的问题,是从事实践必会遇到、必须加以解决的。因此对于这个道德之理的了解虽然容易,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实践并不容易,但不妨碍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实。我想这应该就是“明德”之所以是“明”之意。就是说德性的道理,人只要稍加反省,要求自己能够遵循“应该”而行动,就可以明白。此明德之明亦可从道德之理十分特别或奇特上说。道德之理是以定然令式来表示的,要人无条件行所当行,它不会用现实上的好处、感性上之满足来吸引人,但就足以令人不得不信服,而且努力去遵守。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特别。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有所为而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考虑、算计再给出行动,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何谓道德行动时,就要把所有考虑、算计抛掉,而无条件的只因为是义的缘故而行,这样的要求行动的存心必须是纯粹的道理或原则,是我们自己认为当该遵守的,如果不遵守,就不得不惭愧、内疚。这一种如此特别的道理非常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心中。因此,虽然明德是要通过我们的心知的理解力,才能清楚地为我们所认识,但我们一旦理解或认识到道德之理时,就会肯定这个道理实在十分清楚、明白,是不容置疑的,于是“明”也必须是道德之理本具的特征,即光明昭著是道德之理本身的特性。德性之理本来就是清楚明白,所以很容易被了解,不同于人通过后天经验而认识到的,有关世界的种种知识道理。我想朱子在界定明德时,一定是考虑到道德之理具备上述的特征,而以此特征来理解明德的“明”之意义。明德是指道德之理,即性理,而由于道德之理有上述清楚、明白,又容易被知的性格,所以可以说明德,又可以说虚灵不昧。虚灵虽然是从心知的作用讲,但不昧是重在性理上说的,即是说对于这种非常清楚明白,人不能不承认的道理,是不能够硬说不明白的,即此理是不容自昧的。对于这个道理你若说不明白,那就是自昧甚至是自欺了。但这一种对于性理的清楚明白,只能是上文所说的常知,而不是真知。必须根据此常知进一步对性理做彻底的了解,才可以说是真知。能真知理就能够诚意。所谓诚意,如同朱子在诚意处的注解:“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①所谓“一于善”是把道德上的善作为自己一心一意的行为目标,也可以说是为了善而为善,没有想到为了其他,而这样才可以说是无自欺,就可以无例外地给出道德行为。此即要自己的心完全合于理。
如果此说可通,则明德是性理在于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在心知中,于是这性理本身清楚明白,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看到这理的彰显。人只要反省一下自己对行动存心的要求,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这理的存在。这样讲明德,就表达了人有一种无论是智或愚都能有的对德性的清楚了解,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固然这个根据不是本心,不能如同陆王之学因为觉悟本心就畅通人的德性根源,而给出道德的行为,但亦有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伊川朱子不能如陆王般直接的承体起用,而必须根据这种本有的、对道德的了解作进一步的了解。要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是需要推致心知的作用,但不能够因为朱子重视后天的以心知知理的作用,就说心与理之二是截然为二,理不是心所本知、本具,而且即使心知理,理也只能是所知的对象,不能反身而成为实践道德的动力。推致心知,亦是推致知中之理,亦可说知与理在致知中同时彰显。故可以说,朱子致知格物的道学问工夫是有先天或先验之根据者。
如此的理解明德,我认为可以说明朱子在明德注中所说“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之意,如果像牟先生所说明德是理,则明德何以不论是智愚都未尝息呢?而且明德是本体之明,即是说人人都有此“明”,而且是不会丧失的。这种本体之明当然必须关联到心知来说,虽然关联到心知,但也必须表示这种心知之明是本有的,此明并不是只就心的认识作用来说,而是就对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即上文所说的常知。人人都有这种对于道德之理一般的了解,一反省就显明出来,谁也不能自昧,于是朱子所说的明德之明,是就本来就了解理来说的,即“知”不只是理解力或认识能力,而是对理有本来的认识了解。故当朱子说:“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①时,这个知所识的是理,知与理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致知是就心知对于理的本来了解推而致之。虽然“致知在格物”是表示心知要通过对事事物物的穷格,才可以对理有充分的了解,但这是在以心本知理为基础下,通过格物而要求对理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可以这样说,则格物致知的确如朱子《大学章句·格致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此所谓已知之理,是就上文所说的对于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来说。如果可以这样解说,则格物致知是从对于道性理一般的了解进至极致的了解。并不是在不知理的情况下,通过穷格事物之理而取得道德之理的知识。
四、据《大学或问》说明朱子对“明德”的理解
我认为上文对朱子之“明德说”的解释,应可以成立。在朱子的《大学或问》中,有些文字明白表示此意:
“然则此篇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①
据此段朱子所理解的明德,固然重理,但乃是兼理与气,即必须关联到心来说,此处心是主体,由于有心的主宰性的作用,理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他从人得五行之秀,故人有虚灵的心,而在心中万理咸备。固然之所以会以心为贵,是由于心能具理而彰显理,故明德之德,当然重在理,但由于人有灵明的心,故理在心中本来就可以得到彰显,于是这就是如上文所说的成德的超越根据,故致知之知是有对理的本知作为根据,致知就是从已知进至真知。人本来就有对道德之理的本知,这就是人比其他动物可贵的地方。而根据这一对性理的本知,人就可以做到如同圣人般参天地、赞化育。固然参赞是最后才能达到的境界,但成圣的根据,人人本有。据此可知朱子是从人人都有由五行之秀、正通之气构成的可以具众理的心来说人之可贵。如上引文所说“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故朱子所理解的人之所贵,在于人具有本知理的心。有此心,就有此理。他是关联到心知与理两者,即有此心就有性理来说人之可贵,并不是单说心或单说理为人所有来说人之可贵。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确定朱子所说的明德是心、理二者关联在一起,虽然是二者相关联,但必须是先验的及必然的关联在一起的。当然,由于心、理为二,故此本知理而与理关联在一起的心,并不是即是理的实体性的本心,而且心知理的程度,须用工夫来加强。需要对性理(道德之理)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真知,故后文续云:
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成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②
朱子此段反复说明德于人是本有的,一般人或下愚者因为气质的限制、私欲的蒙蔽,使本有的明德不容易彰显;但虽如此,明德还是有表现出来的可能,故曰“明德未尝息”,这就可以证朱子认为即使是下愚者,明德还是可以在其生命中表现出来。朱子所说的明德,虽然不等于陆王所说的心即理的本心,而是在心知中有性理的明白彰显,心与理虽然为二,但这种明德的彰显,虽在下愚也是可能的。此即表达了上文所说的明德作为成德的超越根据之意,也可以证朱子的成德理论或工夫论,是如同程伊川所说的人本有常知,可以根据此常知进到真知的地步。虽然程朱都强调后天的格物致知工夫,但此工夫是有先天本有的对于德性的本知作为根据的。上引文朱子认为不管是何人,即使是昏昧之极者,即下愚之人,在其情绪未发之时,都可以有明德洞然,即明德彰显之时,虽然其彰显可能是非常短的时间。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凡是人都可以有明德彰显之时,而这就是人成德的根据所在。当然这个成德的可能或超越根据,并不能如陆王或孟子所说的本心良知,只要把此心体扩充,充分实现出来就可以,而必须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格物穷理,虽然如此,格物穷理的工夫是有“本体之明”作为根本,并非是全靠后天的认识才能明理。朱子续云:
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此段说明了不论是在大学或是在小学,都是根据本有的明德之明而作教学的工夫。可以说在小学是通过洒扫应对的生活教育来培养明德(“养之于小学之中”的“之”是指明德),在大学则是通过格物致知来使明德进一步彰显,乃至于使心知充分明理,而恢复理的全体的意义,对于理的表里精粗都能了解,也就是心知的全体大用充分明朗。这虽然是从心知与理两方面说,但二者也是关联在一起,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朱子的小学与大学的教学工夫,都是有本有的明德作为根据,通过大学的格物致知的工夫,就可以恢复心的全体,这所谓全体,就是心知对于本知的性理得到完全的了解,这也就同于伊川从常知到真知的程序。而且即使到此地步,也是人人本有的明德之发挥,并非在性分之外,另作增加的、没有本源之事。朱子续云:
向也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①
这是通过自明其明德而新民,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本于原有的明德而自己用工夫,加以进一步彰显,虽然做到充分明明德的地步,也不是对于人人本有的明德有所增加,由此也可见,朱子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而使心知理达到充分明白的地步,只是恢复明德的本体之明,并不是有所增加,这表示心知对于理的充分明白,只是对本来有的做加强的工夫,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本来没有的认识。这一方面肯定对于理本来有所了解的明德人人都有,而且会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主张必须进一步求知,到对于理有真知,才能持久地维持道德的实践,这是朱子强调道问学之意,但不能因为强调道问学,就说朱子不肯定人对道德之理本有所知,以致其格物致知是求理于外的“义外”之论。从以上《大学或问》的说法,可证朱子并非如牟先生所说的,是“后天渐教”的义理型态,由于对明德本有,而且未尝作出肯定,则朱子这一渐教的系统有先天的根据。故朱子的格物致知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通过心知对理的真切了解而恢复本有的明德之全体大用,在人人本有的明德此一意义上说,人的心知本来具理,而性理本来也有其光明的作用。由于心性二而不二,可以这样相互补充地来说。
在《大学或问》论知的一段,很能表达“知”的特殊性: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欲勉强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②
此段说“知”是心之神明,此一说法,比“心者,人之神明”③更进了一步。心是人之神明,而知则是心之神明,表示了“知”是心的最本质的作用。此一表示可以了解明德注所说的“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固然是说心的作用,但可以更确定地说,这是知的妙用。知的作用是所谓“妙众理”,说“妙众理”是比“具众理”更进一步的,这是表达了“知”把理的意义、作用具体表现出来之意。在《大学纂疏》引的《语录》曰:“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第13页)以虚灵来规定心之本体,就表示了此虚灵是知,而知是心之神明之意。据此,此知并不能理解为心、理为二的心之认知作用,而是此知之虚灵,与性理是相关联的,也可以说知中有理,能充分发挥此知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虚灵不昧的作用),则知中的理,就可以彰显出来。由此可证,朱子所说致知,不止是致心之认知作用,而是知与理都在其中。又在“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处,引语录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第32页)此段很能说明上述之意。理是自己本有的,故知理并非知一外在对象,而是将在我之理发出来。如果不是知中含理,或如上文所说,知与理有先验的关联性,是不能如此说的。
以上论明德,认为当以心关联性理而言,而此关联有先验性;实践的客观根据是理,然而心知对于理本有所知,吾人以为这是朱子言明德之本意,但朱子的有关言论,确有使人从心说明德或从性说明德两种解读的可能,由此也可以理解何以朱子之后会有明德如何理解、如何规定的论争,朱子对明德的规定,确有模棱两可处。朝鲜朝的学者李恒老(号华西,1792—1868)认为朱子对于心的看法可以分为“以理言”与“以气言”,而以理言之心就是明德,明德注中所说的虚灵固然是心,但这是以理言之心,故明德须以理来规定,这是所谓“明德是理”之说。虽然他说明德是理,但其实是关联到心来说的理,也表示了理在心中有其作用,故可以说明德。他将朱子明德注中所涉及的心性情三者都说是理。他这一说法在他的弟子中,引发了争论。柳重教(号省斋,1821—1893)对师说作了修正,认为心的“正说”应该还是从气来规定。他的同门金平默(号重庵,1819—1891),与他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他们俩人的门人继续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是朝鲜朝儒学史上后期的一个重要论争。①当时另一名儒田愚(号艮斋,1841—1922)对华西“明德是理”之说大加反对,主张“明德是心”。艮斋对明德之规定,大体同于牟宗三先生之说。这场朝鲜朝之论争与本文所论,可以有对照之作用,但其中论辩颇多曲折,须另作专文来讨论。
五、结论
朱子对明德的理解,由于关联到性理与心知,其意义的确不很清楚,故牟宗三先生严格区分心、理为二,明德只能从性理说,而心知对于理的了解,是通过后天的经验,以认知的作用,使心涵摄理,而这种解释虽然清楚,也符合朱子心、理为二的规定,但心认知地摄取理,是后天的作用,如是,则心的知理是后天的认知,便没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人心的知理就不能够有保证。于是牟先生把朱子的义理形态判为横摄系统,而且是后天的渐教。这种以后天的认识来使心摄具理的形态,虽然强调了心知的经验认知作用,与后天的学习之重要,但没有能够给出心知知理的保证,也不能给出心之明理之后,能够依理而行的实践的动力。如果对朱子成德的理论作这样的衡定,则朱子之学当然是有理论上不足的地方。但据上文吾人所作的有关朱子的明德注的分析,似乎可以证明,明德虽然有心、理二者相关联来理解之意,但心知与性理二者的关联是先验性的关联,
即性理本来在心中就可以明白地昭显出来,而且心知对于性理之知是本有的。由于性理在心中的昭显,即明德,是人人都有的,虽气质昏昧或私欲深重的人,其明德都未尝息,则人可以根据这本有的明德,来进一步格物致知,即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致乎其极”,则此格物致知的工夫,是有本有的明德,即对于理之本知作根据的。故不能是后天的渐教,而是具有先天根据的渐教。如是,则朱子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并非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说法,也不必说是“异质的跳跃”。由于致知是从本有的、对仁义礼智的常知开始,则充分了解而真知性理,当然是可能的,而在格致的过程中,朱子强调此理是我的理,并非从外入,而且在知理时,也会要求自己非要遵照此理而行不可,这种说法及肯定,也是说得通的。于是格物致知以求对理有真知,在真知理时就可以诚意,即要求自己完全按理而行,这也是可能的情况,说明其并不困难。
当然如此说明德与理解朱子的理论形态,并不能与陆王肯定心即理的形态相混,陆王学从本心良知之呈现,体证到此便是天理所在,把此良知本体充分实现,就可以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一工夫进路,当然是简截有力,可以当下给出道德行动或实践的根源及其动力。而伊川朱子根据人对道德的本知、常知,而进一步致知以求对理有真知,这虽然不是当下把不容已的、自发为善的本心体现、扩充出来,但由于所知的是道德的性理,在有本知作根据的情况下,不会造成因为格物穷理而对道德之理作歧出的了解。而且之所以要从本知的道德之理说到太极之理、天理,是要追问道德之理的根源来处,从然追问其所以然。如果“然”是道德之理,而且是在日用中到处表现的明德,如孝悌慈与忠信等,则根据这些理来作所以然的推证,不应该会歧出。不单只不歧出,而且可以因为这种形而上的推证,明白道德之理的根源来处,说明其为存在之理,而增强了人必须依理而行的说服力。故伊川朱子学虽然不是承本心的不容已而起用的工夫,而是通过对于理的了解的加强,来使行动的意志逐渐纯化的作法,但此一作法或工夫,应该也是可以与陆王学并立,而为成德之教另一有效的工夫理论。而且程朱这一进路,对于人的成德而遭遇到的生命上的问题,有不可取代的克治的作用。因为人在要求自己以道德义务作为行动的唯一依据或原则时,人的感性欲求会起来相争,力图要求人在纯粹的践德时,也要照顾感性欲求的需要,于是很容易的,会将无条件实践的存心转成为有条件的,这是上文一再提到之康德所谓的“自然的辩证”,此即人之“根本恶”①,由于有这自然辩证的现象存在,所以康德认为人必须在对道德法则有所了解的情况,进一步对道德之理作哲学的分析,即所谓从一般的对道德的理性的理解,进至哲学的理解。康德说明对于道德之理的从一般的理解到哲学的理解,是成德必须具有的工夫,即道德实践必须求助于学问或哲学。康德此一说法正好帮助我们理解伊川朱子何以不直接从人对道德法则本有了解处,作充分的力图实践的工夫,而要先从事对本知的道德之理作充分的了解。如果此说可通,则伊川与朱子之所以走这种格物致知的道路,认为先致知才能诚意,也有在实践上不得不如此的缘故。
参考文献:
1.[宋]赵顺孙撰,黄坤整理:《大学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2年。
2.[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四部备要》本),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
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宋]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李恒老:《华西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04册,2003年。
7.柳重教:《省斋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23-324册,2004年。
8.田愚:《艮斋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33册,2003年。
9.[美]H.E.Allison,Kant’s Theory ofFree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韩]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
1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
12.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13.亨利·E.阿利森著,陈虎平译:《康德的自由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康德:《道德形上学基本原理》,牟宗三译注《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5.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牟宗三译注《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6.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重要论争续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
17.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8.杨祖汉:《程伊川、朱子“真知”说新诠——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观点看》,《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2期,总第16期(2011年12月),第177~203页。
19.杨祖汉:《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当代儒学研究》第24期(2018年6月),第47~68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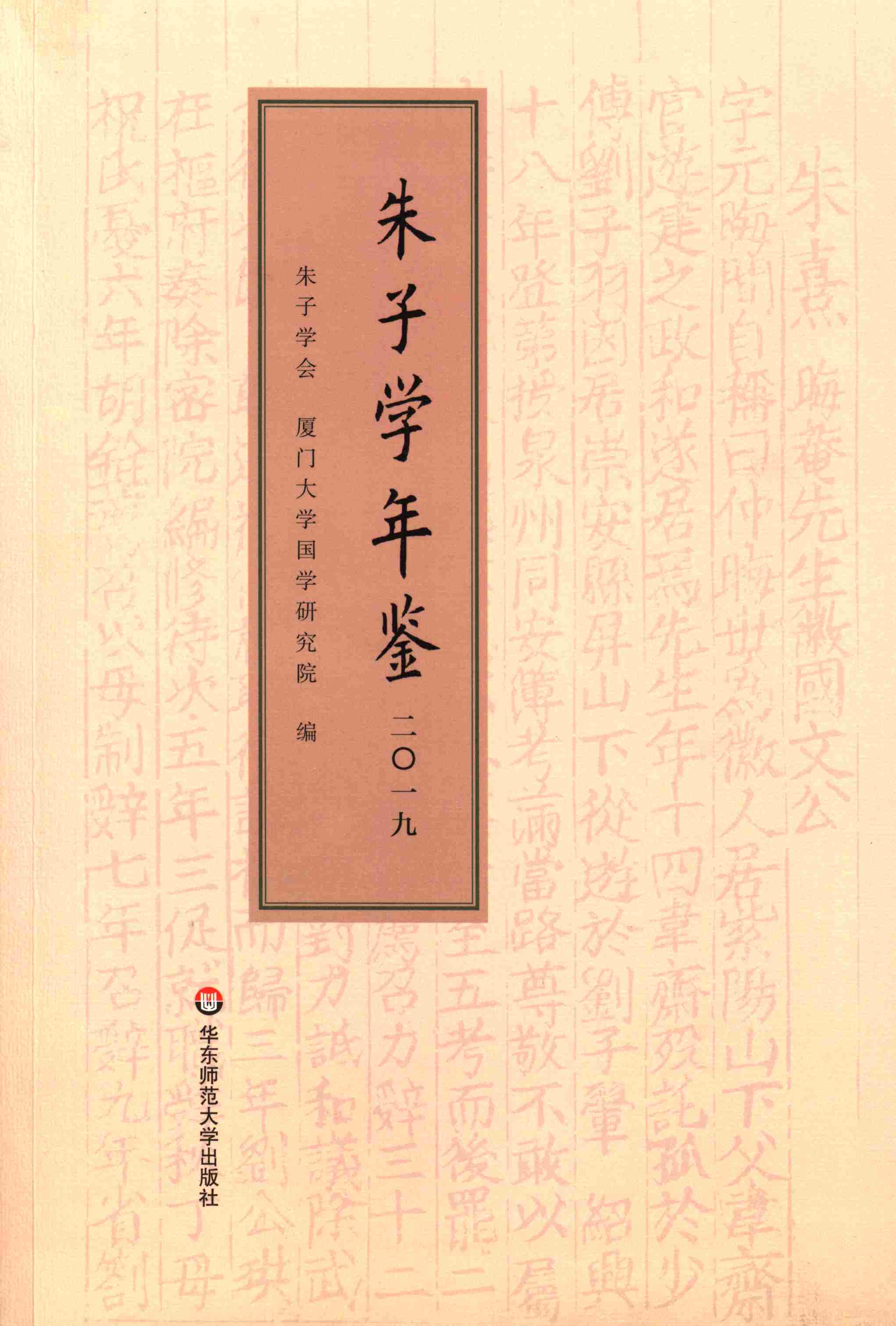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杨祖汉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