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与必然:朱子天理观的再思考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888 |
| 颗粒名称: | 所以与必然:朱子天理观的再思考 |
| 分类号: | B244.75-54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51-061 |
| 摘要: | 朱子在《四书或问》中概括了天理为“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然而在《朱子语类》卷十七中,他进一步解释“所当然”的含义,并将其与“所以然而不可易”联系起来。根据朱子的观点,“所当然”中已经包含了“所以然而不可易”的意思。朱子在《答陈安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概念如所以然、所当然、自然、必然等对于理解朱子的天理观非常关键。在现代汉语语境下重新梳理这些概念的含义,并考察古今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理解朱子的天理概念。其中,朱子对天运有差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天之运行是有差的,这与历法有关。朱子建议将差异纳入历法中,并指出造历时的问题在于界限过窄。他认为天之运行虽无定,但在差错中仍存在一种常度。朱子否定了蔡元定关于天之运无常的观点,并强调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对天之运行确定性的重要性。另外,朱子也关注到实然世界的不齐现象。他指出阴阳的相互作用中会产生不齐的事物,而天地间无尽的阴阳相互转化导致无法达到完全“恰好”的状态。朱子将这种不齐的体现应用到德福之间的不一致上,认为必然中存在不然,但君子应该为善而不计较结果。总的来说,重新梳理朱子关于天理的观点对于更深入理解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天理观 |
内容
在《四书或问》中,朱子将所穷之理概括为“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①。然而《朱子语类》卷十七又载:“或问‘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见得不容已处,则自可默会矣。’”②由此可知,“所当然”之“不容已”当中已经包含了“所以然而不可易”的意思。在《答陈安卿》三(“泰伯篇”)中,针对陈淳“所以《大学章句》、《或问》论难处,惟专以当然不容已者为言,亦此意”的理解,朱子答曰:“《大学》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得不容已处,即自可默会矣。”③这则答问,与前引《语类》一则文字基本一致。按《答陈安卿》三作于1191年④,距《大学或问》成篇已逾十载⑤。朱子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所以然、所当然、自然、必然等概念,是理解朱子天理观的关键。考虑到现代汉语语境的巨大变化,重新梳理这些概念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含义,考察其中的古今之异,对于更深入、准确地把握朱子的天理概念将是不无裨益的。
一、天运有差
认识到天运有差的问题,显然与历法有关。历代制作历法的尝试,都无法做到与天体的运行完全一致。对此,朱子说:
只有季通说得好,当初造历,便合并天运所差之度都算在里。几年后差几分,几年后差几度,将这差数都算做正数,直推到尽头,如此庶几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个大统正,只管说天之运行有差,造历以求合乎天,而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会有差,自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此说极是,不知当初因甚不曾算在里。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运有差”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换言之,天行之差是符合天理的。朱子对蔡元定有关历法的观点的评价,《朱子语类》中有另一则记载,与此正好相反:
季通尝言:“天之运无常。日月星辰积气,皆动物也。其行度疾速,或过不及,自是不齐。使我之法能运乎天,而不为天之所运,则其疏密迟速,或过不及之间,不出乎我。此虚宽之大数纵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无定,自无差也。”季通言非是。天运无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处亦是常度。但后之造历者,其为数窄狭,而不足以包之尔。②
与前引一则不同在于,朱子明确地表达了对蔡元定的批评。但细致比较将会发现,两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一,天之运行是有差的;其二,天行之差自有其常度。天运之差既有常度,则造历时将此常度算入其中,就应该可以与天体运行相一致了。但朱子又明确指出“后之造历者”的问题在于“为数窄狭”。关于“阔”和“窄”的问题,朱子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或问:“康节何以不造历?”曰:“他安肯为此?古人历法疏阔而差少,今历愈密而愈差。”因以两手量桌边云:“且如这许多阔,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阔,便有差。不过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纵使极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测;便有差,容易见。今之历法于这四界内分作八界,于这八界内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则差数愈远。何故?以界限密而逾越多也。”③
从这则议论可知,朱子并不认为可以完全精确地计算出天行之差,只是要这差误落在预先确定的界限内。这样的好处在于容易推测,差处也易见。天之运行既然无法完全精确地计算,则根本上讲还是无定的。朱子之所以不能完全认同蔡元定“天之运无常”的说法,恐怕还是考虑到了天之运行的确定性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简单强调“天运无定”,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人的生活经验中最具确定性的东西。所以,一方面要看天之行度的无定,又要看到其差错当中的“常度”。事实上,天之运行既在大化流行的总体当中,其“无定”是理所当然的:
问:“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天运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①
朱子并不认为地是不动的。地随天而转,只是人在地中,无法觉察其运动而已。天行有差,以致地亦有差。
二、不齐
始终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的实然世界,自然有种种“不齐”:
又问:“一阴一阳,宜若停匀,则贤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驳杂,如何得齐!且以扑钱譬之:纯者常少,不纯者常多,自是他那气驳杂,或前或后,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阴或晴,或风或雨,或寒或热,或清爽,或鹘突,一日之间自有许多变,便可见矣。”又问:“虽是驳杂,然毕竟不过只是一阴一阳二气而已,如何会恁地不齐?”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两个单底阴阳,则无不齐。缘是他那物事错揉万变,所以不能得他恰好。”②
如果天地间只有“两个单底阴阳”,即使相互作用、感应,也不会生出不齐之物。但天道生生不已,阴阳总在不断相互转化当中,阳之动必生阴之静,阴之静又感应出阳之动,无尽日新的阴阳两体,“错揉万变”,所以不可能有完全“恰好”的物事。
气的世界的“不齐”,有方方面面的体现。当然,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德福之间的不一致上:
问:“夫子不答南宫适之问,似有深意。”曰:“如何?”过谓:“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终身为旅人是也;亦有恶如羿奡而得其终者,盗跖老死于牖下是也。凡事应之必然,有时而或不然。惟夫子之圣,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为其所当为,而不计其效之在彼。”(《蜀录》云:“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学者之心,惟知为善而已,他不计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圣人不能如是。”)曰:“此意思较好。”③
“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不是朱子本人的话,是弟子王过的体会。从朱子的回应看,他是认同王过的观点的。这里的“凡事应之必然,有时而或不然”,提示出道学话语中的“必然”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之间的不同。有一物则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关联的某一物,或做这事儿就必定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的必然在两宋道学的世界观里是不存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笼罩性影响,从根本上宰制了当代人的世界观。自然科学的规律被普遍当作必然的铁律。而实际上,自然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并没有在思理的层面上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证明。
三、所以与所以然
自程子以“所以”强调性地区分形上、形下,“所以”和“所以然”就成为天理概念的基本内涵。然而,“所以”一词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具体含义,仍然有含糊之处。“所以”一词在朱子那里,大体上有三种用法:其一,引出某一现象的原因。如,“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灒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①。其二,用以、用来之义。如,“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书所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其何可废!”②其三,决定义。如,“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③。最后这种用法是理解天理概念的关键,但“决定”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决定”,还有待深思。
在朱子那里,“所以然”基本上都是与知相关联的:
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④
这则语录中的“所以然”指道德规范的根据和自然现象的原因,是格物致知的目标。在朱子看来,道德实践能否真正落在实处,是由知的深浅决定的。“所以然”更多地指向道德行为背后的根据。“所以然”既然是知的内容,其中虽然包含对天理的认识,但严格说来,我们不能说天理就是万物的所以然。因为天理并不依赖于人的认知。
“所以然”有时也被表达为“所以当然”。在解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时,朱子即将“天命”解释为“事物所以当然之故”:
又云:“天命处,未消说在人之性。且说是付与万物,乃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须知父子只是一个人,慈孝是天之所以与我者。”⑤
既然强调天之“付与”,“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就有了普遍、决定的意思。
四、当然与自然
朱子讲“当然”,常与“自然”关联在一起:
(炎录云:“天下事合恁地处,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带得安之理来;“朋友信之”,是他自带得信之理来;“少者怀之”,是他自带得怀之理来。圣人为之,初无形迹。季路颜渊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络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带得此理来。①
“合恁地处”即是“当然”。而天下事的“当然”就是“自然之理”的体现。“穿牛鼻,络马首”是对待牛、马的“当然”,同时也就是牛、马的“自然”。“自然”又有“必然”之义:
(砺录云:“毕竟是阳长,将次并进。”)以至于极,则有朋来之道而无咎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消长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处阴之极,乱者复治,往者复还,凶者复吉,危者复安,天地自然之运也。②
在朱子的哲学中,阴阳消长最具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因此,此处的“自然”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必然义的。在后面的讨论中,会有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对于《周易·节卦·彖传》中的“天地节而四时成”,朱子有一段值得注意的阐发:
天地转来,到这里相节了,更没去处。今年冬尽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这里厮匝了,更去不得。这个折做两截,两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节,初无人使他。圣人则因其自然之节而节之,如“修道之谓教”,“天秩有礼”之类,皆是。天地则和这个都无,只是自然如此。③
“到这里厮匝了”是说进入到了一个往复循环当中。“更去不得”的说法,与朱子讨论无极、太极之“极”时的话基本一致:“无极之真是包动静而言,未发之中只以静言。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没去处。濂溪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如‘皇极',亦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辐凑,更没去处;移过这边也不是,移过那边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凑到这里。”④天运循环的“更去不得”与太极、无极之“极”的“更没去处”,皆是“自然”。这里的“自然”,无疑更具必然的意味。朱子既强调“自然之节”是“无人使他”的,则“自然”就有不为别的因素支配和影响的意思。这对于我们理解朱子哲学中的必然义和主宰义是极有帮助的。在朱子与其弟子的讨
论中,有时也用“合当如此”说“当然”: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①
这段话是朱子弟子杨道夫所说。从朱子的回答看,朱子只是对其中“天地无心”的说法有保留。“四时行,百物生”是天道之必然,杨道夫却将其理解为“合当如此”。由此可知,“当然”也有必然义。
五、不容已与必然
朱子说“不容已”,大体上有两种含义:其一,不应该不如此;其二,天运自然意义上的不得不如此。后一种含义更具哲学的意义: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②
这里谈到的“不容已”有非常突出的必然含义。这种必然意义上的“不容已”在朱子论及历史的理势时,是与“自然”、“必然”等概念完全等同起来的:
问:“其所阙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损,固事势之必然。但圣人于此处得恰好,其他人则损益过差了。”曰:“圣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极盛,故秦兴必降杀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变为强戾;周恁地纤悉周致,故秦兴,一向简易无情,直情径行,皆事势之必变。但秦变得过了。秦既恁地暴虐,汉兴,定是宽大。故云:‘独沛公素宽大长者。’秦既鉴封建之弊,改为郡县,虽其宗族,一齐削弱。至汉,遂大封同姓,莫不过制。贾谊已虑其害,晁错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谊之说施之武帝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无非划削宗室,至此可谓极矣。晋武起,尽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势,不得不然。”贺孙问:“本朝大势是如何?”曰:“本朝监五代,藩镇兵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惰弛之余,势有不容已者,但变之自不中道。”③
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子厚论封建是否?”曰:“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过。如廖氏所论封建,排子厚太过。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
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①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得不然”的“事势”或“自然之理势”与“不得已之势”的区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就有个“想做而不能做、不想做却偏又不得不做”的被动意思。之所以有此被动,是仅仅知道历史趋势的无法阻挡,而不知其中的义理之当然。“不得不然”则是真实见到了历史趋势中的“当然”。比如封建,是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对“有功”者、“有德”者、“有亲”者合当有的德义,不是仅仅出于力所不及和治理的需要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至于周末文盛柔弱变而为秦之简易强戾,秦之暴虐转为汉之宽大,则是极则必反的必然之理的体现。到了这里,“更去不得”,所以只能转向相反的方向。
在充满各种“不齐”的气的世界里,阴阳之间的循环消长是“天生自然铁定”②的。天理就是这“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的“所以”:
问:“屈伸往来,气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来者,是理必如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其所以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者,乃道也。”③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今曰“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一阖一辟谓之变”,亦然。④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朱子哲学话语中“所以”的几种含义。这里的“所以”应该是决定的意思。朱子特别指出《易传》所说的不是“阴阳之谓道”,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的道或理是一阴一阳循环不已的决定者、主宰者。值得深思的是:这里的决定和主宰是什么意义上的呢?理又是如何主宰和决定气的流行的呢?
六、主宰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朱子论及天理的本质的相关概念——“当然”、“自然”、“必然”、“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互使用的,且都有与“不容已”和“不得不”的意思关联起来的用法。而这样一种必然的意味又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必然不同:
问:“‘道不可离’,只言我不可离这道,亦还是有不能离底意思否?”曰:
“道是不能离底。纯说是不能离,不成错行也是道!”①
道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必然。如果是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必然,就根本谈不上对错了。朱子所说的“不能离”,只能在无法摆脱的形式和倾向的意义上来理解:
问:“‘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耳。'真、妄是于那发处别识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视听、思虑、动作皆是天理。其顺发出来,无非当然之理,即所谓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虽是妄,亦无非天理,只是发得不当地头。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为草木固无以异,只是那地头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意。”②
“妄者”也是自然倾向的体现,也具有当然的形式,只是发在了不恰当的地方。当羞恶时全无羞恶之心,不当羞恶处却羞恶了。以行道为志向,却以恶衣恶食为耻。羞恶之心是人普遍的自然倾向、善的具体形式之一,发错了地方,就流为恶了。
基于对“必然”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朱子所说的“主宰”的真正含义:
“不窥密”,止“无测未至”。曰:“许多事都是一个心,若见得此心诚实无欺伪,方始能如此。心苟涣散无主,则心皆逐他去了,更无一个主。观此,则求放心处,全在许多事上。将许多事去拦截此心教定。”③
“主”就是不受他者影响和左右,就有个“定”的意思。而“定”就是“不易”,也就是保持自身的同一。而“定”和“不易”又不是僵死的、无变化的,反而是在变化当中,方能恒常的。朱子论《恒卦》曰:
恒,非一定之谓,故昼则必夜,夜而复昼;寒则必暑,暑而复寒,若一定,则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今日道合便从,明日不合则去。又如孟子辞齐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馈,皆随时变易,故可以为常也。④
恒常贯通于变易。或者说,同一是贯通在差异的不断作用和产生当中的。普遍和必然的同一,不受不断产生的差异的影响和左右。
七、理、神与一
在朱子的哲学里,理是主宰者:
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①
问:“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未有人时,此理何在?”曰:“也只在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勺,或取得一担,或取得一碗,都是这海水。但是他为主,我为客,他较长久,我得之不久耳。”②
在天或理与人的关系中,人是被动的。这一被动性根本上源自天对人的“付与”。在朱子那里,天或理的主宰义、主动义和恒久义是确定无疑的。理与神是同等层次的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神不是“鬼神”这个概念层面的神:
问:“所谓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③
理作为形而上者,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④神妙万物。昼夜、阴阳皆为神所变,而神却并不为昼夜、阴阳所变:
问“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曰:“此说‘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此自有个神在其间,不属阴,不属阳,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且如昼动夜静,在昼间神不与之俱动,在夜间神不与之俱静。神又自是神,神却变得昼夜,昼夜却变不得神。神妙万物。如说‘水阴根阳,火阳根阴',已是有形象底,是说粗底了。”⑤
神既不为昼夜所变,则是始终如一的。“神又自是神”,神贯通于一切对立的两体当中,始终自身同一。朱子对张载的“一物两体”说极为赞赏,以为“‘神化’二字,虽程子说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来”⑥。对于张载的“一故神,两故化”,朱子阐发说:
两所以推行乎一也。张子言:“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谓此两在,故一存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或几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后,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后一段,此便是两。如寒,则暑便在其中;昼,则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⑦
“先”的自身同一,已包含“后”。“寒”的自身同一,已包含“暑”。一切差异皆是对立的两体的体现,而对立的两体在各自的自身同一中,已必定包含了对方。“一”不是独立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体之外的“一”。无分别的“一”只能是始终处在无分别的僵死状态,这样的“一”并不存在。“一”只是对立的两体各自的自身同一。而两体中的任何一方的自身同一,同时就意味着对立一方的存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①
动静、阴阳并没有一个开端,所以,程子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对此,朱子明确说道:“这不可说道有个始。他那有始之前,毕竟是个甚么?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坏了后,又恁地做起来,那个有甚穷尽?”②有形之物即使大如天地,终有坏灭。然而,坏灭并不是一切对立和差别的消失。所以,朱子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③这里所说的“水火”,应该只是阴阳二者。阴中涵阳,则有水之象;阳中涵阴,则有火之象。无穷无尽的大化流行,只是相互依存的对立两体的相互作用和转化的体现。然而两体之“立”,又各是其自身同一的体现:“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个,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④
阳之自身同一必以阴为条件,反之亦然。所以,对立两体各自的自身同一,又是对立一方的自身同一的根本。由对立的两体构成的无限差异“推行乎此一”。无限的差异各自的自身同一相互感应、作用,就产生出万变“不齐”的世间万有。天理不是别的,就是遍在于对立的两体以及由两体构成的无限差异的“一”,所以朱子说:“若理,则只是个洁净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⑤所谓的“洁净空阔”,就是纯一无杂之义。理不是别有一物,“分付”和“主宰”万物。理只是一切差异和存有的自身同一。实有的世界虽然万变“不齐”,但总体而言又自有其“定”处:“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⑥这“定”处,就是万有之自身同一的体现。
八、结语
朱子的形上学思想与程子、周子的渊源,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而关于朱子对张载的本体论的汲取,也许是囿于理本与气本的僵化分别,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张载的本体论建构,朱子一方面继承了程子对“清虚一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一物两体”的思想做了创造性的深入阐释和发展。而这一深化、发展对于朱子的天理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朱子的哲学中,气的世界里的具体存有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必然规律。换言之,气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不齐”的。其二,对立的两体(如阴阳、动静)之间的消长、转化的必然性,其实是理的必然性的体现。消长、转化是永恒和必然的,而具体的过程则是或然的、没有确定性的。其三,天理作为形上者,其实就是一切层面的存有和一切存有的层面自身同一的倾向。对立的两体的每一方在维持其自身同一的同时,也在维持其对立面的自身同一。在这个意义上,同一和差异是互为条件的。由此而来的大化流行的统体,才能维持其变化和生生的自身同一,才能永恒变化、生生不已。天理就是“洁净空阔”的“一”。这“一”遍在于一切差异和变化当中。一切差异和变化都是“一”的推行和实现。天理的主宰义和决定义即在于此。“所以”、“当然”、“必然”的根本义涵亦根源于此。
(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所以然、所当然、自然、必然等概念,是理解朱子天理观的关键。考虑到现代汉语语境的巨大变化,重新梳理这些概念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含义,考察其中的古今之异,对于更深入、准确地把握朱子的天理概念将是不无裨益的。
一、天运有差
认识到天运有差的问题,显然与历法有关。历代制作历法的尝试,都无法做到与天体的运行完全一致。对此,朱子说:
只有季通说得好,当初造历,便合并天运所差之度都算在里。几年后差几分,几年后差几度,将这差数都算做正数,直推到尽头,如此庶几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个大统正,只管说天之运行有差,造历以求合乎天,而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会有差,自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此说极是,不知当初因甚不曾算在里。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运有差”是“天之运行合当如此”。换言之,天行之差是符合天理的。朱子对蔡元定有关历法的观点的评价,《朱子语类》中有另一则记载,与此正好相反:
季通尝言:“天之运无常。日月星辰积气,皆动物也。其行度疾速,或过不及,自是不齐。使我之法能运乎天,而不为天之所运,则其疏密迟速,或过不及之间,不出乎我。此虚宽之大数纵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无定,自无差也。”季通言非是。天运无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处亦是常度。但后之造历者,其为数窄狭,而不足以包之尔。②
与前引一则不同在于,朱子明确地表达了对蔡元定的批评。但细致比较将会发现,两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一,天之运行是有差的;其二,天行之差自有其常度。天运之差既有常度,则造历时将此常度算入其中,就应该可以与天体运行相一致了。但朱子又明确指出“后之造历者”的问题在于“为数窄狭”。关于“阔”和“窄”的问题,朱子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或问:“康节何以不造历?”曰:“他安肯为此?古人历法疏阔而差少,今历愈密而愈差。”因以两手量桌边云:“且如这许多阔,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阔,便有差。不过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纵使极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测;便有差,容易见。今之历法于这四界内分作八界,于这八界内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则差数愈远。何故?以界限密而逾越多也。”③
从这则议论可知,朱子并不认为可以完全精确地计算出天行之差,只是要这差误落在预先确定的界限内。这样的好处在于容易推测,差处也易见。天之运行既然无法完全精确地计算,则根本上讲还是无定的。朱子之所以不能完全认同蔡元定“天之运无常”的说法,恐怕还是考虑到了天之运行的确定性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简单强调“天运无定”,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人的生活经验中最具确定性的东西。所以,一方面要看天之行度的无定,又要看到其差错当中的“常度”。事实上,天之运行既在大化流行的总体当中,其“无定”是理所当然的:
问:“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天运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①
朱子并不认为地是不动的。地随天而转,只是人在地中,无法觉察其运动而已。天行有差,以致地亦有差。
二、不齐
始终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的实然世界,自然有种种“不齐”:
又问:“一阴一阳,宜若停匀,则贤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驳杂,如何得齐!且以扑钱譬之:纯者常少,不纯者常多,自是他那气驳杂,或前或后,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阴或晴,或风或雨,或寒或热,或清爽,或鹘突,一日之间自有许多变,便可见矣。”又问:“虽是驳杂,然毕竟不过只是一阴一阳二气而已,如何会恁地不齐?”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两个单底阴阳,则无不齐。缘是他那物事错揉万变,所以不能得他恰好。”②
如果天地间只有“两个单底阴阳”,即使相互作用、感应,也不会生出不齐之物。但天道生生不已,阴阳总在不断相互转化当中,阳之动必生阴之静,阴之静又感应出阳之动,无尽日新的阴阳两体,“错揉万变”,所以不可能有完全“恰好”的物事。
气的世界的“不齐”,有方方面面的体现。当然,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德福之间的不一致上:
问:“夫子不答南宫适之问,似有深意。”曰:“如何?”过谓:“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终身为旅人是也;亦有恶如羿奡而得其终者,盗跖老死于牖下是也。凡事应之必然,有时而或不然。惟夫子之圣,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为其所当为,而不计其效之在彼。”(《蜀录》云:“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学者之心,惟知为善而已,他不计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圣人不能如是。”)曰:“此意思较好。”③
“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不是朱子本人的话,是弟子王过的体会。从朱子的回应看,他是认同王过的观点的。这里的“凡事应之必然,有时而或不然”,提示出道学话语中的“必然”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之间的不同。有一物则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关联的某一物,或做这事儿就必定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的必然在两宋道学的世界观里是不存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笼罩性影响,从根本上宰制了当代人的世界观。自然科学的规律被普遍当作必然的铁律。而实际上,自然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并没有在思理的层面上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证明。
三、所以与所以然
自程子以“所以”强调性地区分形上、形下,“所以”和“所以然”就成为天理概念的基本内涵。然而,“所以”一词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具体含义,仍然有含糊之处。“所以”一词在朱子那里,大体上有三种用法:其一,引出某一现象的原因。如,“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灒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①。其二,用以、用来之义。如,“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书所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其何可废!”②其三,决定义。如,“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③。最后这种用法是理解天理概念的关键,但“决定”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决定”,还有待深思。
在朱子那里,“所以然”基本上都是与知相关联的:
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④
这则语录中的“所以然”指道德规范的根据和自然现象的原因,是格物致知的目标。在朱子看来,道德实践能否真正落在实处,是由知的深浅决定的。“所以然”更多地指向道德行为背后的根据。“所以然”既然是知的内容,其中虽然包含对天理的认识,但严格说来,我们不能说天理就是万物的所以然。因为天理并不依赖于人的认知。
“所以然”有时也被表达为“所以当然”。在解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时,朱子即将“天命”解释为“事物所以当然之故”:
又云:“天命处,未消说在人之性。且说是付与万物,乃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须知父子只是一个人,慈孝是天之所以与我者。”⑤
既然强调天之“付与”,“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就有了普遍、决定的意思。
四、当然与自然
朱子讲“当然”,常与“自然”关联在一起:
(炎录云:“天下事合恁地处,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带得安之理来;“朋友信之”,是他自带得信之理来;“少者怀之”,是他自带得怀之理来。圣人为之,初无形迹。季路颜渊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络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带得此理来。①
“合恁地处”即是“当然”。而天下事的“当然”就是“自然之理”的体现。“穿牛鼻,络马首”是对待牛、马的“当然”,同时也就是牛、马的“自然”。“自然”又有“必然”之义:
(砺录云:“毕竟是阳长,将次并进。”)以至于极,则有朋来之道而无咎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消长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处阴之极,乱者复治,往者复还,凶者复吉,危者复安,天地自然之运也。②
在朱子的哲学中,阴阳消长最具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因此,此处的“自然”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必然义的。在后面的讨论中,会有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对于《周易·节卦·彖传》中的“天地节而四时成”,朱子有一段值得注意的阐发:
天地转来,到这里相节了,更没去处。今年冬尽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这里厮匝了,更去不得。这个折做两截,两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节,初无人使他。圣人则因其自然之节而节之,如“修道之谓教”,“天秩有礼”之类,皆是。天地则和这个都无,只是自然如此。③
“到这里厮匝了”是说进入到了一个往复循环当中。“更去不得”的说法,与朱子讨论无极、太极之“极”时的话基本一致:“无极之真是包动静而言,未发之中只以静言。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没去处。濂溪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如‘皇极',亦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辐凑,更没去处;移过这边也不是,移过那边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凑到这里。”④天运循环的“更去不得”与太极、无极之“极”的“更没去处”,皆是“自然”。这里的“自然”,无疑更具必然的意味。朱子既强调“自然之节”是“无人使他”的,则“自然”就有不为别的因素支配和影响的意思。这对于我们理解朱子哲学中的必然义和主宰义是极有帮助的。在朱子与其弟子的讨
论中,有时也用“合当如此”说“当然”: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①
这段话是朱子弟子杨道夫所说。从朱子的回答看,朱子只是对其中“天地无心”的说法有保留。“四时行,百物生”是天道之必然,杨道夫却将其理解为“合当如此”。由此可知,“当然”也有必然义。
五、不容已与必然
朱子说“不容已”,大体上有两种含义:其一,不应该不如此;其二,天运自然意义上的不得不如此。后一种含义更具哲学的意义: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②
这里谈到的“不容已”有非常突出的必然含义。这种必然意义上的“不容已”在朱子论及历史的理势时,是与“自然”、“必然”等概念完全等同起来的:
问:“其所阙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损,固事势之必然。但圣人于此处得恰好,其他人则损益过差了。”曰:“圣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极盛,故秦兴必降杀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变为强戾;周恁地纤悉周致,故秦兴,一向简易无情,直情径行,皆事势之必变。但秦变得过了。秦既恁地暴虐,汉兴,定是宽大。故云:‘独沛公素宽大长者。’秦既鉴封建之弊,改为郡县,虽其宗族,一齐削弱。至汉,遂大封同姓,莫不过制。贾谊已虑其害,晁错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谊之说施之武帝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无非划削宗室,至此可谓极矣。晋武起,尽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势,不得不然。”贺孙问:“本朝大势是如何?”曰:“本朝监五代,藩镇兵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惰弛之余,势有不容已者,但变之自不中道。”③
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子厚论封建是否?”曰:“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过。如廖氏所论封建,排子厚太过。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
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①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得不然”的“事势”或“自然之理势”与“不得已之势”的区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就有个“想做而不能做、不想做却偏又不得不做”的被动意思。之所以有此被动,是仅仅知道历史趋势的无法阻挡,而不知其中的义理之当然。“不得不然”则是真实见到了历史趋势中的“当然”。比如封建,是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对“有功”者、“有德”者、“有亲”者合当有的德义,不是仅仅出于力所不及和治理的需要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至于周末文盛柔弱变而为秦之简易强戾,秦之暴虐转为汉之宽大,则是极则必反的必然之理的体现。到了这里,“更去不得”,所以只能转向相反的方向。
在充满各种“不齐”的气的世界里,阴阳之间的循环消长是“天生自然铁定”②的。天理就是这“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的“所以”:
问:“屈伸往来,气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来者,是理必如此。‘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气也,其所以一阴一阳循环而不已者,乃道也。”③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今曰“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一阖一辟谓之变”,亦然。④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朱子哲学话语中“所以”的几种含义。这里的“所以”应该是决定的意思。朱子特别指出《易传》所说的不是“阴阳之谓道”,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的道或理是一阴一阳循环不已的决定者、主宰者。值得深思的是:这里的决定和主宰是什么意义上的呢?理又是如何主宰和决定气的流行的呢?
六、主宰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朱子论及天理的本质的相关概念——“当然”、“自然”、“必然”、“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互使用的,且都有与“不容已”和“不得不”的意思关联起来的用法。而这样一种必然的意味又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必然不同:
问:“‘道不可离’,只言我不可离这道,亦还是有不能离底意思否?”曰:
“道是不能离底。纯说是不能离,不成错行也是道!”①
道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必然。如果是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必然,就根本谈不上对错了。朱子所说的“不能离”,只能在无法摆脱的形式和倾向的意义上来理解:
问:“‘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耳。'真、妄是于那发处别识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视听、思虑、动作皆是天理。其顺发出来,无非当然之理,即所谓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虽是妄,亦无非天理,只是发得不当地头。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为草木固无以异,只是那地头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意。”②
“妄者”也是自然倾向的体现,也具有当然的形式,只是发在了不恰当的地方。当羞恶时全无羞恶之心,不当羞恶处却羞恶了。以行道为志向,却以恶衣恶食为耻。羞恶之心是人普遍的自然倾向、善的具体形式之一,发错了地方,就流为恶了。
基于对“必然”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朱子所说的“主宰”的真正含义:
“不窥密”,止“无测未至”。曰:“许多事都是一个心,若见得此心诚实无欺伪,方始能如此。心苟涣散无主,则心皆逐他去了,更无一个主。观此,则求放心处,全在许多事上。将许多事去拦截此心教定。”③
“主”就是不受他者影响和左右,就有个“定”的意思。而“定”就是“不易”,也就是保持自身的同一。而“定”和“不易”又不是僵死的、无变化的,反而是在变化当中,方能恒常的。朱子论《恒卦》曰:
恒,非一定之谓,故昼则必夜,夜而复昼;寒则必暑,暑而复寒,若一定,则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今日道合便从,明日不合则去。又如孟子辞齐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馈,皆随时变易,故可以为常也。④
恒常贯通于变易。或者说,同一是贯通在差异的不断作用和产生当中的。普遍和必然的同一,不受不断产生的差异的影响和左右。
七、理、神与一
在朱子的哲学里,理是主宰者:
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①
问:“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未有人时,此理何在?”曰:“也只在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勺,或取得一担,或取得一碗,都是这海水。但是他为主,我为客,他较长久,我得之不久耳。”②
在天或理与人的关系中,人是被动的。这一被动性根本上源自天对人的“付与”。在朱子那里,天或理的主宰义、主动义和恒久义是确定无疑的。理与神是同等层次的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神不是“鬼神”这个概念层面的神:
问:“所谓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③
理作为形而上者,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④神妙万物。昼夜、阴阳皆为神所变,而神却并不为昼夜、阴阳所变:
问“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曰:“此说‘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此自有个神在其间,不属阴,不属阳,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且如昼动夜静,在昼间神不与之俱动,在夜间神不与之俱静。神又自是神,神却变得昼夜,昼夜却变不得神。神妙万物。如说‘水阴根阳,火阳根阴',已是有形象底,是说粗底了。”⑤
神既不为昼夜所变,则是始终如一的。“神又自是神”,神贯通于一切对立的两体当中,始终自身同一。朱子对张载的“一物两体”说极为赞赏,以为“‘神化’二字,虽程子说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来”⑥。对于张载的“一故神,两故化”,朱子阐发说:
两所以推行乎一也。张子言:“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谓此两在,故一存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或几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后,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后一段,此便是两。如寒,则暑便在其中;昼,则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⑦
“先”的自身同一,已包含“后”。“寒”的自身同一,已包含“暑”。一切差异皆是对立的两体的体现,而对立的两体在各自的自身同一中,已必定包含了对方。“一”不是独立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体之外的“一”。无分别的“一”只能是始终处在无分别的僵死状态,这样的“一”并不存在。“一”只是对立的两体各自的自身同一。而两体中的任何一方的自身同一,同时就意味着对立一方的存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①
动静、阴阳并没有一个开端,所以,程子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对此,朱子明确说道:“这不可说道有个始。他那有始之前,毕竟是个甚么?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坏了后,又恁地做起来,那个有甚穷尽?”②有形之物即使大如天地,终有坏灭。然而,坏灭并不是一切对立和差别的消失。所以,朱子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③这里所说的“水火”,应该只是阴阳二者。阴中涵阳,则有水之象;阳中涵阴,则有火之象。无穷无尽的大化流行,只是相互依存的对立两体的相互作用和转化的体现。然而两体之“立”,又各是其自身同一的体现:“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个,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④
阳之自身同一必以阴为条件,反之亦然。所以,对立两体各自的自身同一,又是对立一方的自身同一的根本。由对立的两体构成的无限差异“推行乎此一”。无限的差异各自的自身同一相互感应、作用,就产生出万变“不齐”的世间万有。天理不是别的,就是遍在于对立的两体以及由两体构成的无限差异的“一”,所以朱子说:“若理,则只是个洁净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⑤所谓的“洁净空阔”,就是纯一无杂之义。理不是别有一物,“分付”和“主宰”万物。理只是一切差异和存有的自身同一。实有的世界虽然万变“不齐”,但总体而言又自有其“定”处:“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⑥这“定”处,就是万有之自身同一的体现。
八、结语
朱子的形上学思想与程子、周子的渊源,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而关于朱子对张载的本体论的汲取,也许是囿于理本与气本的僵化分别,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张载的本体论建构,朱子一方面继承了程子对“清虚一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一物两体”的思想做了创造性的深入阐释和发展。而这一深化、发展对于朱子的天理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朱子的哲学中,气的世界里的具体存有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必然规律。换言之,气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不齐”的。其二,对立的两体(如阴阳、动静)之间的消长、转化的必然性,其实是理的必然性的体现。消长、转化是永恒和必然的,而具体的过程则是或然的、没有确定性的。其三,天理作为形上者,其实就是一切层面的存有和一切存有的层面自身同一的倾向。对立的两体的每一方在维持其自身同一的同时,也在维持其对立面的自身同一。在这个意义上,同一和差异是互为条件的。由此而来的大化流行的统体,才能维持其变化和生生的自身同一,才能永恒变化、生生不已。天理就是“洁净空阔”的“一”。这“一”遍在于一切差异和变化当中。一切差异和变化都是“一”的推行和实现。天理的主宰义和决定义即在于此。“所以”、“当然”、“必然”的根本义涵亦根源于此。
(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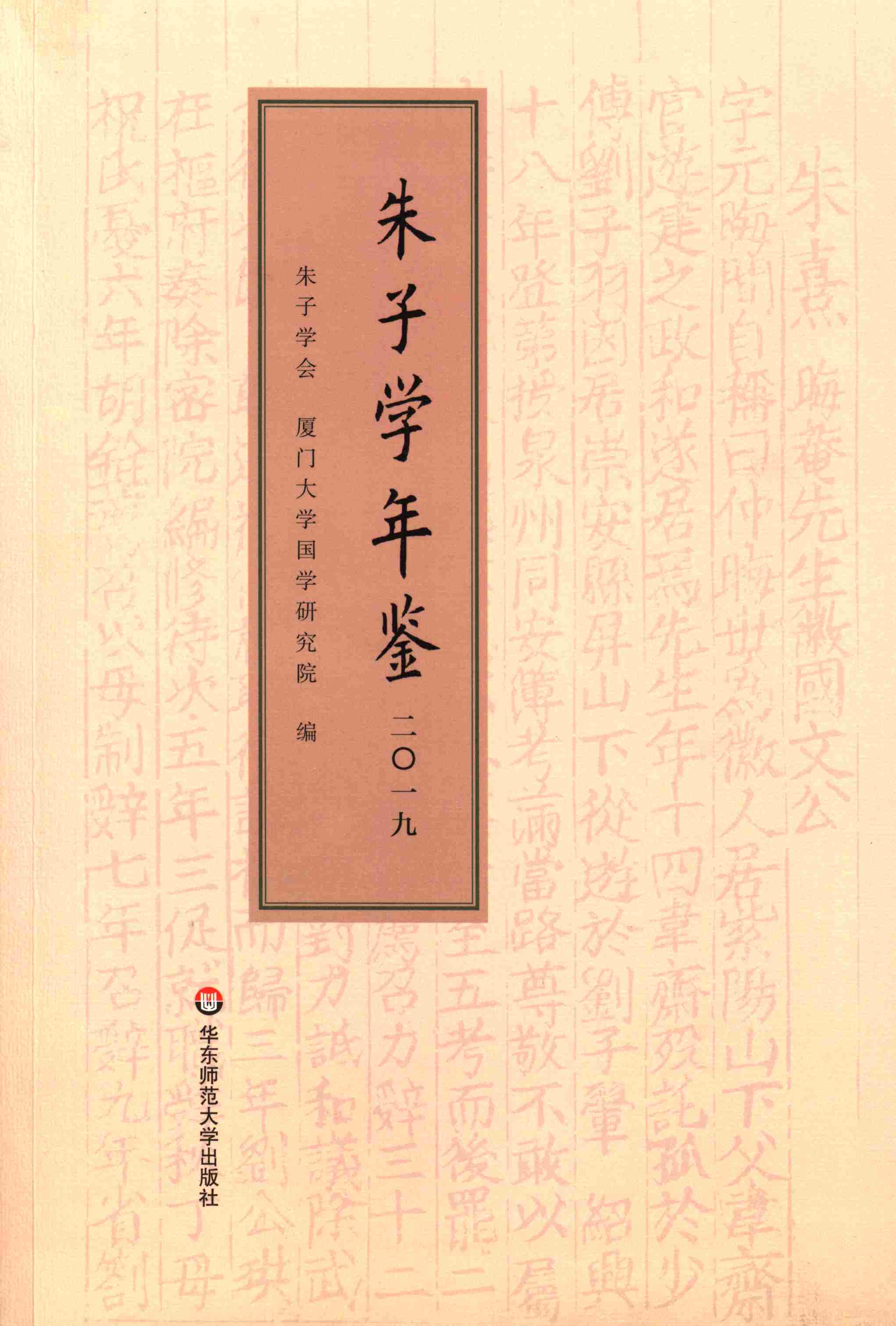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杨立华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