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帝王学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9》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867 |
| 颗粒名称: | 朱熹的帝王学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09-019 |
| 摘要: | 朱熹的帝王学观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士大夫与平天下以及道统论和正统论。朱熹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理想的社会是由圣人组成的集体,当人人明确自己的明德并真诚地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社会就会实现和谐与安定。朱熹强调个人的修养与社会的安定密切相关,每个人都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对天下安定的贡献。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追求“道统”的正统,通达“道统”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在道统论方面,朱熹认为皇帝的合法统治基于政权的正统性,而道统的正统性则基于学理的正统性。朱熹认为儒学的正统应该是道学,认为正统的道学传承自上古圣神,孔子是道学的继承者。他强调道统并非仅仅是政权统治,而是关乎人心、道德和道德性的传授。朱熹的道统论意味着个人可以直接参与道学,并追求道的境界和实践道的原则。在正统论方面,朱熹将政权的正统性与道义性分开。他认识到政权的正统性与道义性之间的不一致,将正统概念从政权的道义性中剥离出来。朱熹的正统论承认政权的正统性,但不将其与道义性挂钩,进一步强调了对学理的正统以及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朱熹的正统论与当时的宋朝特色正统论相呼应,将正统观念与政权分离,强调人心、道义和道德对于正统的重要性。总之,朱熹的帝王学观点着重强调个人修养、追求道的境界和实践,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
| 关键词: | 朱熹 帝王学 士大夫 |
内容
一、士大夫与平天下
朱熹认为,人皆可以成圣,理想的社会就是圣人组成的集体,天下万民各明其明德,平天下就会实现: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11页①)然而,朱熹真的相信这样的世界会到来吗?即使从上古圣王的时代算起,这样的社会都不曾存在过。所以在朱熹看来,个人修养的完善与社会的安定如何关联在一起,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即使成为圣人,天下也不会立刻太平。圣人孔子的时代,“平天下”不也没有实现吗?
如果照字面意思,“平天下”可解释为“安定天下”。每个人都需要成为王者,才可以进行天下的安定统治。但是朱熹的意思并非如此,他在《大学或问》中就此说道:
曰:治国平天下者,天子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盖无与焉。今大学之教,乃例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言。岂不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为为己之学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而非吾心之所当爱,无一事而非吾职之所当为。虽或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其分内也。又况大学之教,乃为天子之元子众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适子,与国之俊选而设。是皆将有天下国家之责而不可辞者,则其所以素教而预养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国家为己事之当然,而预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
(《朱子全书》第6册,第513~514页)
“治国”、“平天下”不是天子诸侯之事吗?——朱熹先提出这个设问,然后做了回答。即所谓“平天下”、“治国”,并非指王和诸侯对天下国家的统治,而是说即使是平民百姓,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对天下安定的贡献。朱熹在说明“性”的时候,常常用官职作比喻。尽自己的职责,就意味着尽“性”。
另外,对于“天职”,朱熹说道: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商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皆其所当尽者。小大虽异,界限截然。本分当为者,一事有阙,便废天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推是心以尽其职者,无以易诸公之论。但必知夫所处之职,乃夭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则各司其职以办其 事者,不出于勉强不得已之意矣。(《朱子语类》卷十三第83条,第235~236页)①
“职”这个词,对于皇帝,对于宰相,都可以使用。
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23-624页) 皇帝、宰相、士大夫,都需要各尽其职。
朱熹的一个接近无穷大的数字。现实中,他所设立的目标,是在有德之君的手下,贤臣云集,民众也一定程度得到教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道学为社会所认知、所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朱熹的道统论
皇帝的皇位得到认可,在于他的王朝是正统的。在日本,正统与道统之间的界限不明;而在中国,基本上“正统”意味着政权的正统性(Legitimacy),“道统”意味着学理的正统性(Orthodoxy)。不过这只是基本用法,有时也存在将“道统”比喻性地称作“正统”的情况。
“正统”一词,在朱熹之前已有使用。汉代班固的《典引》等古代的作品中,已可见到用例。而到了宋代,如众所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章望之等人的正 统论,更是喧腾一时。②
而“道统”一词,在朱熹之前几乎没有使用。③确立“道统”一词的功劳,很大程度还是在朱熹。①尤其《中庸章句序》的“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段话更是广为人知。有关朱熹的道统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儒学内部主张道学的正统,另一个是在道学内部主张自己的正统。
下面讨论朱熹的道统论。从上古圣神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王者以道相传授。这意味着这一阶段道统与正统相重合,而到了并非王者的孔子,道统与正统相分离,孔子成为了单独的道统继承者。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未成为帝王,给儒教埋下了怨恨的种子②;但是反过来看,或许这オ是儒教的幸运。正因为道统从政权问题中脱离出来,オ使得儒教的道不局限于执政者和高官,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直接参与进来。“人皆可以成圣”这个道学的主张,以人人皆可以接受道统为前提。在这里,儒教的学问与修养不再限于统治层,而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出要求。
余英时指出,继承“道统”的王者们既是圣人,又居天子之位,兼具“内圣外王”两面;并且以《中庸章句序》中的“上古圣神”至周公为“道统”的时代,孔子以后为“道学”的时代。③但是笔者认为,孔子以后依然是道统。
这里重要的是,对于正统与道统的具体关系,朱熹几乎从未说起。道统的传人如果必须是王者,那么宋朝皇帝应当继承道统;然而,朱熹虽然要求皇帝理解道,却没有以道统传人作为必要的前提。一度断绝的道统得以重新延续,并非出自皇帝之手,而是有赖于周敦颐和二程。可见,道统的问题脱离了王权而 得以独立。
另外,元朝以后出现了治统论,认为皇帝继承了朱子学的道统;日本则出现了皇统论,主张天皇集道统、正统于一身。④治统论是将道德上并不完美的皇帝,无条件认定为道统的传人,这就削弱了朱子学原本的道德理想主义特点。朱熹的思想对于政权持严格的道德理想主义态度,而这正是依靠正统与道统的 分离而成立的。
对朱熹而言,重要的是,孔子并非王者。最接近孔子的是一介布衣的颜回,士大夫眼中的榜样就是这个颜回。这意味着,“道统”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圣人纯粹成为心境的问题;圣王之间相传的道统,其核心也是尧舜禹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经 大禹谟》)这个道德性的传授。换句话说,“道统”论的本旨在于,上古圣神相传而来的道就是一个心的问 题。这个心的问题可以“平天下”,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侧重点却在于,“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人心。
三、朱熹的正统论
下面讨论朱熹的正统论。一般认为宋代的正统论,发端于因修史和制定朝廷仪礼的需要而对五代各朝正统与否所进行的探讨。以后者为例,由于王朝需 要配以五行之一,所以探讨五代各朝的正统与否,都联系宋朝所对应的五行,从而奠定宋朝仪礼的总基调。
但是宋朝特色的正统论,则起于认识到政权的正统性与道义性的不一致。苏轼有言:“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正统论·辩论二》)①,认为欧阳修是这种正统论的发端,此后苏轼的“名”、“实”之论也在此意义上显得重要。朱熹的正统论将王朝的道义性与“正统”概念截然分开,就是这 种宋朝式正统论的一次体现。②
明确阐述朱熹正统论的,是《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下称《凡例》)。一般认为,《凡例》是朱熹亲笔所作,但是也有人持怀疑的态度。归根结底,从现存资料来看,是否为朱熹亲笔确有怀疑余地,然而也难以断定非朱熹所作。③最终留下的疑问是:朱熹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称《纲目》)表现出异常的执着,既然是该书的《凡例》,朱熹理应在书信等文章中有所提及,而且门人弟子也应对其有所讨论,然而两者都没有。但不管怎样,《凡例》作为朱子学正统论的明确表述受到传承,是不争的事实。
《凡例》的内容直截了当,令人吃惊。成为正统的条件,就是统一天下并维持两代以上。如果取得了天下,而不能传给下一代,则依据“篡贼谓篡位干统而不及传世者”(《凡例·统系》)的规定,只是“篡贼”而已。相反,秦朝虽然焚书坑儒,由于持续了秦始皇、秦二世两代,所以获得正统的认可,隋朝同样也是如此。例如,《纲目》在表述秦始皇去世时,就用了表示天子驾崩的“崩”字(《纲目》卷二,始皇帝三十七年)。
朱子学正统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将蜀国认定为三国时期的正统。一般容易认为,朱熹这样认定是出于道德上的考量;然而实际上,刘备的德行等与此无关,将蜀汉定为正统,仅仅因为刘备是汉朝王室的后裔。也就是说,统一王朝的继承者,即使沦为地方政权,也视为正统。
这里依据《凡例·统系》,将正统、篡贼、无统整理如下:
正统……周、秦、汉、晋、隋、唐。
篡贼……汉之吕后、王莽、唐之武后之类。
无统……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
即使原则上统一天下并维持两代以上是受天命的标志,将秦、隋这种在儒教的立场上难以接受的朝代也视为正统,终究会让人有所抵触。顺便一提,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浅见䌹斋指出,如果秦朝王室尚存,即使汉夺得政权,秦依然是正统(《靖献遗言讲义》卷二《三国正统辨》)。①
另一方面,朱熹似乎又持有三国无统论。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义刚录作:此时便是无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54条,第2626页)
这条语录为陈淳所记,同时黄义刚也在场;根据田中谦二的年代考,这种情况出现在朱熹70至71岁这个人生的最后时期。②按文中的说法,《纲目》也是三国无统论。然而,与此相反,下面的语录显然是蜀汉正统论。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55条,第2637页)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56条,第2637页)前者语录的记录者不明;后者是余大雅,据田中谦二的年代考,是朱熹50至60岁之间的语录。①由此看来,朱熹或是同时兼有蜀汉正统论和无统论,或是由蜀汉正统论变成了无统论。引文后者说,写作《纲目》的动机之一,就是主张蜀汉的正统。现在的《纲目》也是以蜀汉为正统。说他由此变成了无统论,一时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如果蜀汉只是“正统之余”,而非“正统”,同样南宋也被金夺去了北方半壁江山,也不能称之为正统了。这个问题不易解答,只有待于他日另考。
对于正统论中的道义性缺失,明代朱子学者方孝孺提出了质疑。其《释统》(《逊志斋集》卷二)一文的内容,表示如下:
正统一 三代、汉、唐、宋
变统三……“取之不以正” 晋、齐、宋、梁
“守之不以仁义” 秦、隋
“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 符坚、武氏②
这里意识到夷狄政权的问题,可能还是受元朝的影响。朱熹虽然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第49条,第3245页),但是无意将唐朝视为夷狄的朝代;他的正统论中,华夷之别尚不明显。众所周知,唐王朝出身于武川镇军阀,有浓厚的鲜卑血统。另外,方孝孺的分法,就其结果而言,与区分正统和霸统的章望之《明统论》(载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一苏轼《正统论》所附的南宋郎晔注中)相近。③
总之,方孝孺追求朱子学的道德主义,结果对朱熹本人的正统论都进行了批判。然而,如果在正统的条件中要求完美无瑕的道义性,那么即使方孝孺列为正统的汉、唐、宋,其实也不能称为正统(浅见䌹斋《靖献遗言讲义》卷八《正统说》)。④
这让人想起朱熹与陈亮的争论。陈亮认为汉、唐是道已显现的时代,而朱熹予以否认。在朱熹看来,统一天下之时具备完美道义性的朝代,周之后一个也不存在。所以浅见䌹斋为朱熹解释道,他所认为正统的王朝,并不意味道义上也同样完美(浅见䌹斋《靖献遗言讲义》卷八《正统说》、《劄录》)①。道义上完美的朝代,就是如此地难得。既然如此,现实中可以期待的,就只有作为政治主体刷新朝政的士大夫,以及通过帝王学对帝王所做的感化。士大夫的力量将在此参与进来,而先决条件即是将其凝聚在一个共同的对象上;所以正统论在此发挥作用,它决定正统的政权并提供忠诚的对象。
四、朱熹的帝王学
朱熹所生活的南宋,已经成为了地方政权;但既然是对于统一王朝北宋的继承,按照朱熹的规定,依然是正统。人们需要向南宋朝廷尽忠,正是由于它是正统的王朝。然而,如前所述,正统的王朝不意味着皇帝就是圣人,所以这里需要帝王学的登场。
朱熹与陈亮之间那场著名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政治的安定是否可以视作道的实现。朱熹在给陈亮的信中,如此写道:
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朱子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8页)
陈亮认为,汉唐太平之世就其结果而言,道已经显现;而朱熹认为,不具备对道的理解,就不存在道的实现。理解道的前提,是认识到理解道的必要性。有此认识,才可以逐步向理想的状态前进;无此认识,政治上的成果永远都只是一时偶合而已。“心”对于帝王而言非常重要,就此朱熹说道:
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这篇文章是光宗即位,下诏广求意见(淳熙十六年),60岁的朱熹应此准备上奏的奏章。结果,朱熹并没有上奏。就其原因,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说道:
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除秘阁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朱子全书》第27册,第550页)
即因为朝中有道学的敌对势力,所以没有上奏。朱熹意识到敌对势力而放弃上奏,反过来看,不正意味着这篇奏章中可能有浓厚的道学色彩吗?
这篇奏章由十条建议组成:
一、讲学以正心
二、修身以齐家
三、远便嬖以近忠直
四、抑私恩以抗公道
五、明义理以绝神奸
六、择师傅以辅皇储
七、精选任以明体统
八、振纲纪以厉风俗
九、节财用以固邦本
十、修政事以攘夷狄(原注:按前总目,此处当有“修政事以攘夷狄”一条,今缺。)
第一、二条是学问与修养,第三条是用人。朱熹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皇帝抱有期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皇帝致力于学问与修养,意味着他对于道的觉醒。在朱熹看来,皇帝在道上觉醒,任用贤相,进而使民众得到教化,就是安定天下的第一方略。换句话说,拥有最高用人权的皇帝准确地用人,才可以使朝政得到刷新。
皇帝用人的得当与否,取决于皇帝自身的见识。为培养这种见识,士大夫能做的,就是提供帝王学。程颐在《论经筵劄子》三(《程氏文集》卷六)的“贴黄”中说:
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①在这里经筵能与宰相并提,就是因为它是传授帝王学的地方。
朱熹也在《通书解·治第十二》中,对于人才任用有如下强调: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从也。(周敦颐原文:“心纯则贤才辅。”)
众贤各任其职,则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周敦颐原文:“贤才辅则天下治。”)
心不纯,则不能用贤。不用贤,则无以宣化。(周敦颐原文:“纯心要矣,用贤急焉。”)②
余英时指出,士大夫的政治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③一是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辅佐君主统治天下;二是成为地方官,重建局部的秩序,直接“泽民”。并且朱熹等道学家,原本倾向于后者(余英时又说,道学家也具有在中央辅佐君主的愿望)。朱熹担任地方官时的努力,尤其社仓法的实施等,可谓其代表性事例。然而笔者认为,更应该考虑的是,道学所具有的帝王学的一面。道学家们向皇帝靠近,除了具体政策的实现之外,更为期待的是指引皇帝,让他认识到“平天下”的基础就在于心,从而使得以宰相为首的人选得到合理任用,而各项政策也都从此心的立场出发开展。现实中,程颐等成为皇帝之师的例子,给了道学家鼓舞。他们热衷于向皇帝直言,或是直接奔向帝王的怀抱。
道学以帝王学提供者的方式受到瞩目,促进了其势力的扩大。程颐以崇政殿说书的身份,成为了哲宗的侍讲。旧法党士大夫被王安石排斥出中央之时,他们深刻认识到神宗任用王安石这种人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所以当他们重回中央之后,就重视对年幼的哲宗进行帝王学教育,从而将身为布衣的程颐拔擢为侍讲。这为道学在士大夫中间树立帝王学形象奠定了基础。后来程颐的弟子尹焞,也担任了崇政殿说书。
朱熹针对神宗用人的影响之大,如此说道: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可惜,可惜。(《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第15条,第3046页)朱熹又盛赞神宗为“大有为之主”,并说如果任用了程颢,会取得很大的成果。
神庙,大有为之主,励精治道,事事要理会过。是时却有许多人才。若专用明道为大臣,当大段有可观。明道天资高,又加以学,诚意感格,声色不动,而事至立断。当时用人参差如此,亦是气数舛逆。(《朱子语类》卷七十二第75条,第1832页)
在朱熹看来,任用王安石还是程颢,决定了政治的走向。
朱熹的帝王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是《书经·大禹谟》的人心道心之传,一个是《大学》。《大禹谟》说明尧、舜、禹帝王之间所相传的是心法,在与陈亮的争论中,这一点也得到了突显。帝王学是磨炼帝王的心法,道学正在这一点上发挥作用。
其一所谓讲学以正心者,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另外,《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的是从天子到平民都需要修身。《大学》是一部象征着从皇帝到平民都经由同样的阶梯,向圣人努力的书。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八条目的路程,皇帝与士大夫一同前行。宁宗即位,朱熹受命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年65岁,在《行宫便殿奏劄》二(《朱子文集》卷十四)中,向皇帝阐述格物穷理的必要性之后说道:
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在此基础上,又说道:
此数语者,皆愚臣平生为学艰难辛苦已试之效。窃意圣贤复生,所以教人不过如此。不独布衣韦带之士所当从事。盖虽帝王之学殆亦无以易之。特以近年以来,风俗薄陋,士大夫间闻此等语,例皆指为道学,必排去之而后已。(《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布衣韦带之士”即普通士人之学,与帝王之学初无二致;对这一点的强调,值得我们注意。朱熹又如下说道:
须得人主如穷阎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讲明义理,以此应天下之务,用天下之才,方见次第。(《朱子语类》卷七十二第75条,第1832页)
这里“人主”也只与“穷阎陋巷之士”一般;皇帝和士大夫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修养与学问。皇帝学习《大学》,意味着与士大夫共享同一个前进的阶梯;士大夫也好,皇帝也好,都从“格物”出发,走向“平天下”。
朱熹在《己酉拟上封事》中,强调必须上正纲纪、下厉风俗的同时,又指出为此需要的是宰执、台谏、人主都各尽其职。
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25页)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角色,政治才可以良好运行。
另外,余英时指出,相对于《大学》,朱熹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更多引用尧舜禹“人心”、“道心”之传等《书经》中有关王者的内容。①但是需要注意,“格物”、“正心”在奏章中也有所强调。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孝宗即位,33岁的朱熹上书了《壬午应诏封事》。文中朱熹先引用《书经·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明了王者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于当年重视“记诵华藻”,以及老、释的“虚无寂灭”之害做了批评,之后说道: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至于孔子,集厥大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故承议郎程颢与其弟颐崇政殿说书,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皆以为此篇乃孔氏遗书,学者所当先务。诚至论也。(《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2页)
这里朱熹强调了《大学》的“格物致知”在帝王学中的重要性,并说阐明这一点的正是道学。第二年,朱熹又在《癸未垂拱奏劄》中说道:
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此所谓大学之道,虽古之大圣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学乎此者。尧舜相授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此也。(《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1页)可以看到,《大学》与《书经》中“危微精一”之语直接联系在一起。朱熹65岁向宁宗进讲时,虽说出于上意,但所讲内容正是《大学》。实际上对于皇帝而言,帝王学是令人厌烦的;程颐和朱熹做侍讲时,其毫不妥协的态度,分别让哲宗和宁宗最终都疏远了他们。帝王学是向周围旁观的士大夫所做的一种宣传。在皇帝看来,帝王学是一个负担;而在士大夫看来,却令人欢欣鼓舞。
朱熹帝王学的特色在于,正统和道统分开之后,对于道德性得不到保证的皇帝,要求与士大夫从事相同的学问和修养,以此促使皇帝实现道学理想的用人。皇帝与士大夫都从各自的立场,践行《大学》的八条目。这里存在一种分工,但君臣之间又得以产生君臣一体的感觉。朱熹的帝王学,正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所构建的帝王学,所以士大夫社会可以显示出其存在感。
朱熹认为,人皆可以成圣,理想的社会就是圣人组成的集体,天下万民各明其明德,平天下就会实现: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11页①)然而,朱熹真的相信这样的世界会到来吗?即使从上古圣王的时代算起,这样的社会都不曾存在过。所以在朱熹看来,个人修养的完善与社会的安定如何关联在一起,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即使成为圣人,天下也不会立刻太平。圣人孔子的时代,“平天下”不也没有实现吗?
如果照字面意思,“平天下”可解释为“安定天下”。每个人都需要成为王者,才可以进行天下的安定统治。但是朱熹的意思并非如此,他在《大学或问》中就此说道:
曰:治国平天下者,天子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盖无与焉。今大学之教,乃例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言。岂不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为为己之学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而非吾心之所当爱,无一事而非吾职之所当为。虽或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其分内也。又况大学之教,乃为天子之元子众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适子,与国之俊选而设。是皆将有天下国家之责而不可辞者,则其所以素教而预养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国家为己事之当然,而预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
(《朱子全书》第6册,第513~514页)
“治国”、“平天下”不是天子诸侯之事吗?——朱熹先提出这个设问,然后做了回答。即所谓“平天下”、“治国”,并非指王和诸侯对天下国家的统治,而是说即使是平民百姓,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对天下安定的贡献。朱熹在说明“性”的时候,常常用官职作比喻。尽自己的职责,就意味着尽“性”。
另外,对于“天职”,朱熹说道: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商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皆其所当尽者。小大虽异,界限截然。本分当为者,一事有阙,便废天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推是心以尽其职者,无以易诸公之论。但必知夫所处之职,乃夭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则各司其职以办其 事者,不出于勉强不得已之意矣。(《朱子语类》卷十三第83条,第235~236页)①
“职”这个词,对于皇帝,对于宰相,都可以使用。
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23-624页) 皇帝、宰相、士大夫,都需要各尽其职。
朱熹的一个接近无穷大的数字。现实中,他所设立的目标,是在有德之君的手下,贤臣云集,民众也一定程度得到教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道学为社会所认知、所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朱熹的道统论
皇帝的皇位得到认可,在于他的王朝是正统的。在日本,正统与道统之间的界限不明;而在中国,基本上“正统”意味着政权的正统性(Legitimacy),“道统”意味着学理的正统性(Orthodoxy)。不过这只是基本用法,有时也存在将“道统”比喻性地称作“正统”的情况。
“正统”一词,在朱熹之前已有使用。汉代班固的《典引》等古代的作品中,已可见到用例。而到了宋代,如众所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章望之等人的正 统论,更是喧腾一时。②
而“道统”一词,在朱熹之前几乎没有使用。③确立“道统”一词的功劳,很大程度还是在朱熹。①尤其《中庸章句序》的“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段话更是广为人知。有关朱熹的道统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儒学内部主张道学的正统,另一个是在道学内部主张自己的正统。
下面讨论朱熹的道统论。从上古圣神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王者以道相传授。这意味着这一阶段道统与正统相重合,而到了并非王者的孔子,道统与正统相分离,孔子成为了单独的道统继承者。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未成为帝王,给儒教埋下了怨恨的种子②;但是反过来看,或许这オ是儒教的幸运。正因为道统从政权问题中脱离出来,オ使得儒教的道不局限于执政者和高官,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直接参与进来。“人皆可以成圣”这个道学的主张,以人人皆可以接受道统为前提。在这里,儒教的学问与修养不再限于统治层,而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出要求。
余英时指出,继承“道统”的王者们既是圣人,又居天子之位,兼具“内圣外王”两面;并且以《中庸章句序》中的“上古圣神”至周公为“道统”的时代,孔子以后为“道学”的时代。③但是笔者认为,孔子以后依然是道统。
这里重要的是,对于正统与道统的具体关系,朱熹几乎从未说起。道统的传人如果必须是王者,那么宋朝皇帝应当继承道统;然而,朱熹虽然要求皇帝理解道,却没有以道统传人作为必要的前提。一度断绝的道统得以重新延续,并非出自皇帝之手,而是有赖于周敦颐和二程。可见,道统的问题脱离了王权而 得以独立。
另外,元朝以后出现了治统论,认为皇帝继承了朱子学的道统;日本则出现了皇统论,主张天皇集道统、正统于一身。④治统论是将道德上并不完美的皇帝,无条件认定为道统的传人,这就削弱了朱子学原本的道德理想主义特点。朱熹的思想对于政权持严格的道德理想主义态度,而这正是依靠正统与道统的 分离而成立的。
对朱熹而言,重要的是,孔子并非王者。最接近孔子的是一介布衣的颜回,士大夫眼中的榜样就是这个颜回。这意味着,“道统”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圣人纯粹成为心境的问题;圣王之间相传的道统,其核心也是尧舜禹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经 大禹谟》)这个道德性的传授。换句话说,“道统”论的本旨在于,上古圣神相传而来的道就是一个心的问 题。这个心的问题可以“平天下”,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侧重点却在于,“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人心。
三、朱熹的正统论
下面讨论朱熹的正统论。一般认为宋代的正统论,发端于因修史和制定朝廷仪礼的需要而对五代各朝正统与否所进行的探讨。以后者为例,由于王朝需 要配以五行之一,所以探讨五代各朝的正统与否,都联系宋朝所对应的五行,从而奠定宋朝仪礼的总基调。
但是宋朝特色的正统论,则起于认识到政权的正统性与道义性的不一致。苏轼有言:“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正统论·辩论二》)①,认为欧阳修是这种正统论的发端,此后苏轼的“名”、“实”之论也在此意义上显得重要。朱熹的正统论将王朝的道义性与“正统”概念截然分开,就是这 种宋朝式正统论的一次体现。②
明确阐述朱熹正统论的,是《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下称《凡例》)。一般认为,《凡例》是朱熹亲笔所作,但是也有人持怀疑的态度。归根结底,从现存资料来看,是否为朱熹亲笔确有怀疑余地,然而也难以断定非朱熹所作。③最终留下的疑问是:朱熹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称《纲目》)表现出异常的执着,既然是该书的《凡例》,朱熹理应在书信等文章中有所提及,而且门人弟子也应对其有所讨论,然而两者都没有。但不管怎样,《凡例》作为朱子学正统论的明确表述受到传承,是不争的事实。
《凡例》的内容直截了当,令人吃惊。成为正统的条件,就是统一天下并维持两代以上。如果取得了天下,而不能传给下一代,则依据“篡贼谓篡位干统而不及传世者”(《凡例·统系》)的规定,只是“篡贼”而已。相反,秦朝虽然焚书坑儒,由于持续了秦始皇、秦二世两代,所以获得正统的认可,隋朝同样也是如此。例如,《纲目》在表述秦始皇去世时,就用了表示天子驾崩的“崩”字(《纲目》卷二,始皇帝三十七年)。
朱子学正统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将蜀国认定为三国时期的正统。一般容易认为,朱熹这样认定是出于道德上的考量;然而实际上,刘备的德行等与此无关,将蜀汉定为正统,仅仅因为刘备是汉朝王室的后裔。也就是说,统一王朝的继承者,即使沦为地方政权,也视为正统。
这里依据《凡例·统系》,将正统、篡贼、无统整理如下:
正统……周、秦、汉、晋、隋、唐。
篡贼……汉之吕后、王莽、唐之武后之类。
无统……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
即使原则上统一天下并维持两代以上是受天命的标志,将秦、隋这种在儒教的立场上难以接受的朝代也视为正统,终究会让人有所抵触。顺便一提,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浅见䌹斋指出,如果秦朝王室尚存,即使汉夺得政权,秦依然是正统(《靖献遗言讲义》卷二《三国正统辨》)。①
另一方面,朱熹似乎又持有三国无统论。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义刚录作:此时便是无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54条,第2626页)
这条语录为陈淳所记,同时黄义刚也在场;根据田中谦二的年代考,这种情况出现在朱熹70至71岁这个人生的最后时期。②按文中的说法,《纲目》也是三国无统论。然而,与此相反,下面的语录显然是蜀汉正统论。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55条,第2637页)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第56条,第2637页)前者语录的记录者不明;后者是余大雅,据田中谦二的年代考,是朱熹50至60岁之间的语录。①由此看来,朱熹或是同时兼有蜀汉正统论和无统论,或是由蜀汉正统论变成了无统论。引文后者说,写作《纲目》的动机之一,就是主张蜀汉的正统。现在的《纲目》也是以蜀汉为正统。说他由此变成了无统论,一时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如果蜀汉只是“正统之余”,而非“正统”,同样南宋也被金夺去了北方半壁江山,也不能称之为正统了。这个问题不易解答,只有待于他日另考。
对于正统论中的道义性缺失,明代朱子学者方孝孺提出了质疑。其《释统》(《逊志斋集》卷二)一文的内容,表示如下:
正统一 三代、汉、唐、宋
变统三……“取之不以正” 晋、齐、宋、梁
“守之不以仁义” 秦、隋
“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 符坚、武氏②
这里意识到夷狄政权的问题,可能还是受元朝的影响。朱熹虽然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第49条,第3245页),但是无意将唐朝视为夷狄的朝代;他的正统论中,华夷之别尚不明显。众所周知,唐王朝出身于武川镇军阀,有浓厚的鲜卑血统。另外,方孝孺的分法,就其结果而言,与区分正统和霸统的章望之《明统论》(载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一苏轼《正统论》所附的南宋郎晔注中)相近。③
总之,方孝孺追求朱子学的道德主义,结果对朱熹本人的正统论都进行了批判。然而,如果在正统的条件中要求完美无瑕的道义性,那么即使方孝孺列为正统的汉、唐、宋,其实也不能称为正统(浅见䌹斋《靖献遗言讲义》卷八《正统说》)。④
这让人想起朱熹与陈亮的争论。陈亮认为汉、唐是道已显现的时代,而朱熹予以否认。在朱熹看来,统一天下之时具备完美道义性的朝代,周之后一个也不存在。所以浅见䌹斋为朱熹解释道,他所认为正统的王朝,并不意味道义上也同样完美(浅见䌹斋《靖献遗言讲义》卷八《正统说》、《劄录》)①。道义上完美的朝代,就是如此地难得。既然如此,现实中可以期待的,就只有作为政治主体刷新朝政的士大夫,以及通过帝王学对帝王所做的感化。士大夫的力量将在此参与进来,而先决条件即是将其凝聚在一个共同的对象上;所以正统论在此发挥作用,它决定正统的政权并提供忠诚的对象。
四、朱熹的帝王学
朱熹所生活的南宋,已经成为了地方政权;但既然是对于统一王朝北宋的继承,按照朱熹的规定,依然是正统。人们需要向南宋朝廷尽忠,正是由于它是正统的王朝。然而,如前所述,正统的王朝不意味着皇帝就是圣人,所以这里需要帝王学的登场。
朱熹与陈亮之间那场著名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政治的安定是否可以视作道的实现。朱熹在给陈亮的信中,如此写道:
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朱子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8页)
陈亮认为,汉唐太平之世就其结果而言,道已经显现;而朱熹认为,不具备对道的理解,就不存在道的实现。理解道的前提,是认识到理解道的必要性。有此认识,才可以逐步向理想的状态前进;无此认识,政治上的成果永远都只是一时偶合而已。“心”对于帝王而言非常重要,就此朱熹说道:
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这篇文章是光宗即位,下诏广求意见(淳熙十六年),60岁的朱熹应此准备上奏的奏章。结果,朱熹并没有上奏。就其原因,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说道:
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除秘阁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朱子全书》第27册,第550页)
即因为朝中有道学的敌对势力,所以没有上奏。朱熹意识到敌对势力而放弃上奏,反过来看,不正意味着这篇奏章中可能有浓厚的道学色彩吗?
这篇奏章由十条建议组成:
一、讲学以正心
二、修身以齐家
三、远便嬖以近忠直
四、抑私恩以抗公道
五、明义理以绝神奸
六、择师傅以辅皇储
七、精选任以明体统
八、振纲纪以厉风俗
九、节财用以固邦本
十、修政事以攘夷狄(原注:按前总目,此处当有“修政事以攘夷狄”一条,今缺。)
第一、二条是学问与修养,第三条是用人。朱熹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皇帝抱有期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皇帝致力于学问与修养,意味着他对于道的觉醒。在朱熹看来,皇帝在道上觉醒,任用贤相,进而使民众得到教化,就是安定天下的第一方略。换句话说,拥有最高用人权的皇帝准确地用人,才可以使朝政得到刷新。
皇帝用人的得当与否,取决于皇帝自身的见识。为培养这种见识,士大夫能做的,就是提供帝王学。程颐在《论经筵劄子》三(《程氏文集》卷六)的“贴黄”中说:
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①在这里经筵能与宰相并提,就是因为它是传授帝王学的地方。
朱熹也在《通书解·治第十二》中,对于人才任用有如下强调: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从也。(周敦颐原文:“心纯则贤才辅。”)
众贤各任其职,则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周敦颐原文:“贤才辅则天下治。”)
心不纯,则不能用贤。不用贤,则无以宣化。(周敦颐原文:“纯心要矣,用贤急焉。”)②
余英时指出,士大夫的政治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③一是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辅佐君主统治天下;二是成为地方官,重建局部的秩序,直接“泽民”。并且朱熹等道学家,原本倾向于后者(余英时又说,道学家也具有在中央辅佐君主的愿望)。朱熹担任地方官时的努力,尤其社仓法的实施等,可谓其代表性事例。然而笔者认为,更应该考虑的是,道学所具有的帝王学的一面。道学家们向皇帝靠近,除了具体政策的实现之外,更为期待的是指引皇帝,让他认识到“平天下”的基础就在于心,从而使得以宰相为首的人选得到合理任用,而各项政策也都从此心的立场出发开展。现实中,程颐等成为皇帝之师的例子,给了道学家鼓舞。他们热衷于向皇帝直言,或是直接奔向帝王的怀抱。
道学以帝王学提供者的方式受到瞩目,促进了其势力的扩大。程颐以崇政殿说书的身份,成为了哲宗的侍讲。旧法党士大夫被王安石排斥出中央之时,他们深刻认识到神宗任用王安石这种人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所以当他们重回中央之后,就重视对年幼的哲宗进行帝王学教育,从而将身为布衣的程颐拔擢为侍讲。这为道学在士大夫中间树立帝王学形象奠定了基础。后来程颐的弟子尹焞,也担任了崇政殿说书。
朱熹针对神宗用人的影响之大,如此说道: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可惜,可惜。(《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第15条,第3046页)朱熹又盛赞神宗为“大有为之主”,并说如果任用了程颢,会取得很大的成果。
神庙,大有为之主,励精治道,事事要理会过。是时却有许多人才。若专用明道为大臣,当大段有可观。明道天资高,又加以学,诚意感格,声色不动,而事至立断。当时用人参差如此,亦是气数舛逆。(《朱子语类》卷七十二第75条,第1832页)
在朱熹看来,任用王安石还是程颢,决定了政治的走向。
朱熹的帝王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是《书经·大禹谟》的人心道心之传,一个是《大学》。《大禹谟》说明尧、舜、禹帝王之间所相传的是心法,在与陈亮的争论中,这一点也得到了突显。帝王学是磨炼帝王的心法,道学正在这一点上发挥作用。
其一所谓讲学以正心者,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另外,《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的是从天子到平民都需要修身。《大学》是一部象征着从皇帝到平民都经由同样的阶梯,向圣人努力的书。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八条目的路程,皇帝与士大夫一同前行。宁宗即位,朱熹受命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年65岁,在《行宫便殿奏劄》二(《朱子文集》卷十四)中,向皇帝阐述格物穷理的必要性之后说道:
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在此基础上,又说道:
此数语者,皆愚臣平生为学艰难辛苦已试之效。窃意圣贤复生,所以教人不过如此。不独布衣韦带之士所当从事。盖虽帝王之学殆亦无以易之。特以近年以来,风俗薄陋,士大夫间闻此等语,例皆指为道学,必排去之而后已。(《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布衣韦带之士”即普通士人之学,与帝王之学初无二致;对这一点的强调,值得我们注意。朱熹又如下说道:
须得人主如穷阎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讲明义理,以此应天下之务,用天下之才,方见次第。(《朱子语类》卷七十二第75条,第1832页)
这里“人主”也只与“穷阎陋巷之士”一般;皇帝和士大夫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修养与学问。皇帝学习《大学》,意味着与士大夫共享同一个前进的阶梯;士大夫也好,皇帝也好,都从“格物”出发,走向“平天下”。
朱熹在《己酉拟上封事》中,强调必须上正纲纪、下厉风俗的同时,又指出为此需要的是宰执、台谏、人主都各尽其职。
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25页)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角色,政治才可以良好运行。
另外,余英时指出,相对于《大学》,朱熹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更多引用尧舜禹“人心”、“道心”之传等《书经》中有关王者的内容。①但是需要注意,“格物”、“正心”在奏章中也有所强调。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孝宗即位,33岁的朱熹上书了《壬午应诏封事》。文中朱熹先引用《书经·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明了王者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于当年重视“记诵华藻”,以及老、释的“虚无寂灭”之害做了批评,之后说道: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至于孔子,集厥大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故承议郎程颢与其弟颐崇政殿说书,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皆以为此篇乃孔氏遗书,学者所当先务。诚至论也。(《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2页)
这里朱熹强调了《大学》的“格物致知”在帝王学中的重要性,并说阐明这一点的正是道学。第二年,朱熹又在《癸未垂拱奏劄》中说道:
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此所谓大学之道,虽古之大圣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学乎此者。尧舜相授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此也。(《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1页)可以看到,《大学》与《书经》中“危微精一”之语直接联系在一起。朱熹65岁向宁宗进讲时,虽说出于上意,但所讲内容正是《大学》。实际上对于皇帝而言,帝王学是令人厌烦的;程颐和朱熹做侍讲时,其毫不妥协的态度,分别让哲宗和宁宗最终都疏远了他们。帝王学是向周围旁观的士大夫所做的一种宣传。在皇帝看来,帝王学是一个负担;而在士大夫看来,却令人欢欣鼓舞。
朱熹帝王学的特色在于,正统和道统分开之后,对于道德性得不到保证的皇帝,要求与士大夫从事相同的学问和修养,以此促使皇帝实现道学理想的用人。皇帝与士大夫都从各自的立场,践行《大学》的八条目。这里存在一种分工,但君臣之间又得以产生君臣一体的感觉。朱熹的帝王学,正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所构建的帝王学,所以士大夫社会可以显示出其存在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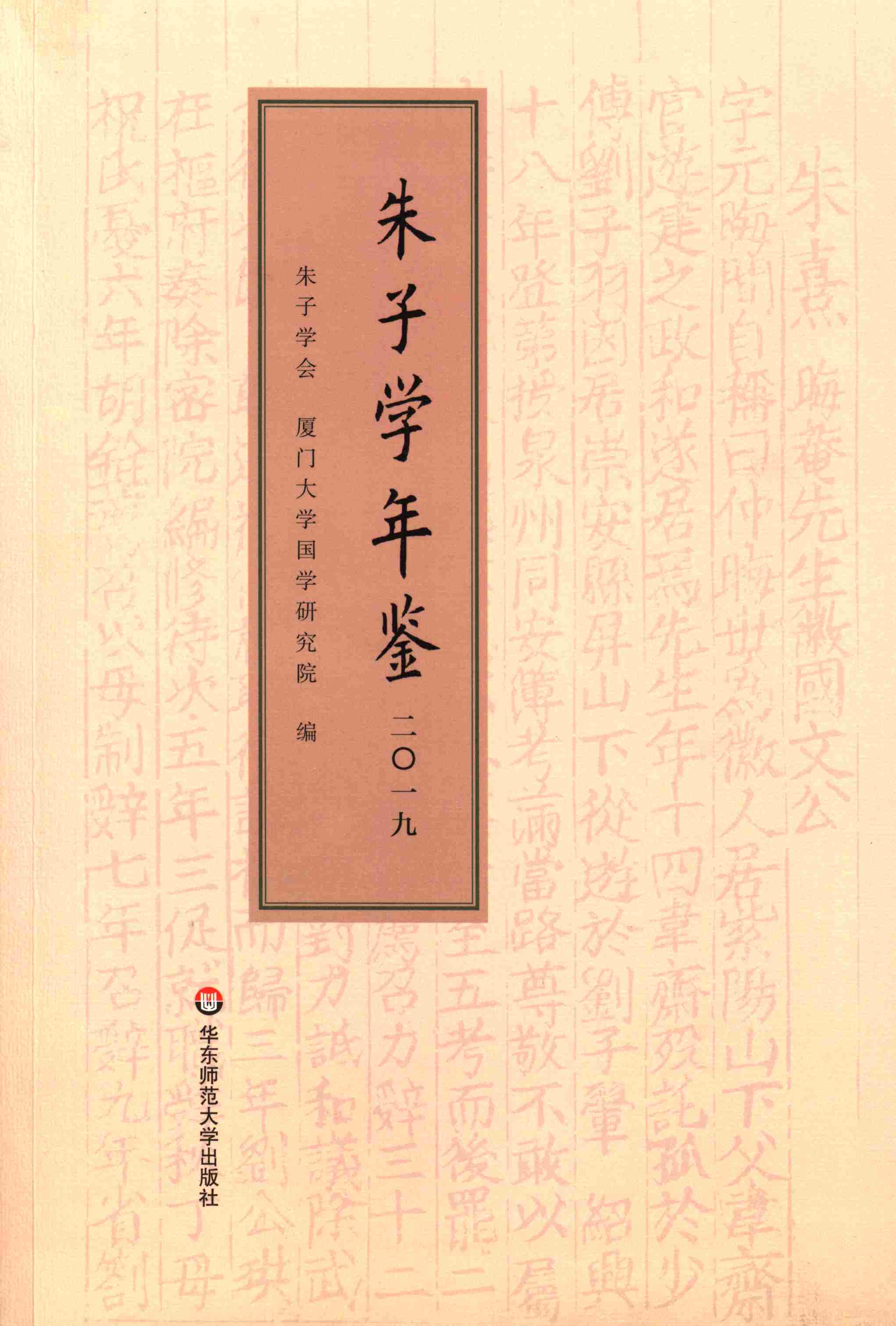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9》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哲学开拓》《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