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 新、社会改革、认识论”会议综述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674 |
| 颗粒名称: | “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 新、社会改革、认识论”会议综述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6 |
| 页码: | 270-275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2015年7月11〜12日,由德国儒学会和德国特利尔大学主办的“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新、社会改革、认识 论”(Zhu Xi and His Efforts for Renewal: Innovation, Social Reform, Epistemology)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特里尔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朱子学研究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围绕“朱子学传承与创新”“朱子学与社会改革”“朱子学的认识论研究”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是一次朱子学的国际性会议,其会议成果代表了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
| 关键词: | 朱子学 传承 创新 |
内容
2015年7月11〜12日,由德国儒学会和德国特利尔大学主办的“朱熹及其复兴努力:创新、社会改革、认识 论”(Zhu Xi and His Efforts for Renewal: Innovation, Social Reform, Epistemology)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特里尔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朱子学研究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围绕“朱子学传承与创新”“朱子学与社会改革”“朱子学的认识论研究”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是一次朱子学的国际性会议,其会议成果代表了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ー、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
作为朱子学的核心,朱熹哲学是在朱熹与他人的反复论辩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在《朱陆之辩:朱熹时代的知识更新与辩论实践》一文中,来自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杜杰庸(Cuillaume Dutoumier )博士,强调了“论辩”在朱熹知识更新实践中的中心地位。杜杰庸从朱陆之辩切入,在研究了朱陆之辩的相关材料后,指明了隐藏在两位文人思想家关系背后的思想分化过程。杜杰庸认为,在朱陆之辩中,观念的相互作用暗示了一种文本的实用取向(a pragmatic approach ),基于此,杜杰庸试图坚持主位(emic )的观点,旨在形成对当时学术活动中论辩模式的更好理解。
作为ー套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哲学具有独特的哲学范畴与哲学问题。在《论朱子思想中人“心”之定位》一文中,来自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锦枝指出,朱子思想中的人“心”即不能说是“理”,也不能说是“气”,这种非理非气的定位使朱熹预先规避了心学可能产生的流弊,具有独特的价值。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金刚,着重分析了朱熹哲学中“气禀为何在源头上就有不齐”的问题。在《朱子论气运之不齐》一文中,赵金刚指出,万物之生并不是“ー齐生”,每个具体存在都有自己从创生到毁灭的过程。由是,不同的根据理而生、按照理而动的气之间便产生了摩擦,这样一来,动与静、主动与被动永恒地纠葛在ー起,无端无始,流行的气运之不齐也就因此产生。所以,朱子认为气运从源头上就有不齐,而这源头无它,即气之为气,气以理为根据而存在。朱子对理气的论述不仅实现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ー,也实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ー。
作为ー种东亚现象,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也独具特色,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哲学问题。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就对韩国大儒李栗谷的“人心道心”问题做了细致分疏。在《精微之境: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一文中,谢晓东指出,李栗谷对“人心”“道心”概念的界定具有两种主要视角:形上学视角和动机视角。在人心、道心的价值属性上,李栗谷始终如一地认为道心是纯善的,而对人心的价值属性判断则经历了从恶到不是恶再到有善有恶的演变。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上,李栗谷经历了从对立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到统ー论(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转变,其转变的关节点是1572年夏天栗谷与牛溪的论辩。谢晓东认为,李栗谷人心道心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两种善问题,即道心与人心之善是否为同一种善?解决这 ー理论困难的最佳方案有赖于回归朱 熹的人心通孔说。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财富,朱子学的当代研究也是生机盎然。在会上,德国波恩学者陈琦向我们介绍了德语区宋明理学的研究情况。陈琦指出,汉学大师福克(Alfred Forke ) 于1927〜1938年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德语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书中首次大量翻 译宋明理学经典的重要段落。福克将朱子学说分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四个部分,并视朱子为可以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莱布尼茨相提并论的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此之后,德语地区陆续都有关于朱熹研究的专著出版,而21世纪的前十年在经典名著翻译与评注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此外,朱熹的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当代朱子学研究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会上,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汇报了《朱子语类》合刊本的编修计划。朱杰人指出,《徽州刊朱子语类》早于黎靖德的咸淳刻本,而作为《徽州刊朱子语类》的摹写本,《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简称“古写本”)区别于黎靖德咸淳刻本系统,而具有独立的文献价值。然而,学界却一直将古写本作为现存成化本[1]的校勘本,这不仅破坏了《徽州刊朱子语类》的原貌,而且也不能突出它存在的意义。因此,为了更直观全面地展示《朱子语类》的重要文献价值,将古写本与成化本编纂为《朱子语类》合刊本对世界朱子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朱子学与社会改革
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演绎着儒家哲学内圣外王的基本逻辑。在外王层面上,朱子学作为ー种文化现象,必然勾连着社会多方面的改革内容,而其中礼学更是对社会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胡秀娟博士在《朱熹和士庶通礼》一文中指出,朱熹的《家礼》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礼的应用已经从“礼不下庶人”转变成为“士庶通礼”。相较于司马光与程颐,朱熹《家礼》在冠、婚、丧、祭四方面对士庶通礼的损益内容,使得此后的礼仪与“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文化迥然有别。当然,朱熹并非一味注重从简从俗从众,他始终坚持对古礼进行适宜有度的去取折中,这对当时礼义亡阙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然而,来自中国浙江大学哲学系的衷鑫恣博士认为,道学实现的某些社会变革却反过来导致了道学为人所不喜甚或痛恨不绝如缕的现象。第一,道学将早期儒学的士人之教扩至士庶全体之教,这样一来,俗众普遍地视礼教为枷锁就会使道学大受敌意;第二,程朱以来,道学家之间好以讲学为事,风气相许,渐渐形成无形的道统集团,如此,势必被当权者所嫉,而终使政治与民间对道学的反对声汇流。
包括朱子礼学在内的宋代礼学,其特点之一便是注重“礼”之义理的阐发,这与汉代礼学注重“礼”之考据的学术风气迥然不同。正是由于这ー不同,清代礼学形成了汉宋之争。在《试析清儒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ーー以〈论语后案〉为例》一文中,中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肖永明和陈峰,将黄式三的《论语后案》视为清儒以“礼”解经的典范之作,并对其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做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黄式三所著的《论语后案》以郑玄礼学为学问宗主,在重视三《礼》与《论语》互证的基础上以《周礼》为正。与仅以考证言“礼”的汉学家不同,黄式三更加注重礼意的建构,其治经既釆纳汉学所擅长的经史考证之学,同时也吸收宋学注重义理建构的长处,试图以礼学统摄汉宋学术,从而消泯门户之争。从肖永明和陈峰的文章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礼学似乎是中国文化的ー个ー贯之处。
朱子学不但对东亚各国的传统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朱子学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来自美国的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与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便在会上探讨了朱熹哲学与普世价值的问题。他们以《朱子家训》为中心,介绍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在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中推广《朱子家训》的历程,同时也分析了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与儒家学者对待普世价值的敌意态度。田浩与田梅指出,在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无须对讨论普世价值如此敏感和防卫,而西方亦应理解中国终会对“普世”做出调整或改变,将独特性融入普世性中,并可能影响全球。随着中国不断地权力集中化和提高全球地位,中国的学者和大众知识分子会继续受到政治统一和全球地位提升的影响。他们会重新注释普世宗教,亦会重新注释普世价值,这些“普世性”定会附上特定的中国痕迹和特点。
在朱熹哲学的成长过程中,以 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儒家一直是作为朱熹哲学的反对者而存在着的。德国波恩学者史克礼(Christian Schweirnann )在会上发表了《功利主义儒家的起源:荀子如何发现经济》一文,文章从田浩《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对陈亮功利主义的探讨岀发,将功利主义儒家的起源追溯到荀子。通过对《荀子•富国》的分析,史克礼指出,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以前,荀子就已提出劳动分工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协作是“上下俱富”的重要手段。在这里,荀子事实上是基于ー个分配正义的观念而提出了剩余财富的再分配。对于君王而言,荀子认为君王应当为了社会财富的流通而储存余粮且刺激经济,由此方能使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整个国家利益最大化。从史克礼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儒家的理论亦蕴含了对社会改革的诸多有益因素。
三、朱子学的认识论研究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是朱子学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它代表着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来自法国西巴黎大学的戴鹤白 (RogerDarrobers)指出,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原文的补注,是其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长期思考并提炼升华的结果。在回答门人有关“格物致知”问题的诸多答文中,朱熹为阐释《大学》中的知识起源论而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要素。在《朱熹对“理”这ー范畴的发展是认识论上的ー个进 步吗? ——从先秦儒家的“道”论出发评析》一文中,来自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杜仑认为,朱熹混淆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对主体自己,特别是主体的“伦理原则”认识的区别。除此之外,朱熹把道德观念形而上化为“理”,提出了认知和保存“理”的道心等概念,虽然继承发展了先秦的“知行观”,却不仅减低了天作为至上神在人类道德修养中的作用,而且也限制了人类在发展自己道德观念中的主动性。
事实上,对于朱熹“格物致 知”思想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在《诗歌视域下的朱熹认识论》 (Zhu Xi s Epistemology in Light of His
Foeり)一文中,来自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宇指出,朱熹留下的大量诗作对于更好地理解其格物致知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朱熹必须要面对那种以华丽辞藻描绘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自发情感的诗歌传统。此类诗歌因其所带有佛道的超越倾向,故与朱熹通过格物致知在此世寻“道”的认识论有所抵触。在朱熹与此类诗歌的斗争过程中,外在世界、内在情感和哲学倾向间的张力在朱熹的诗歌中被强化了,同时其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也更为集中和敏感,这便使得诗歌能够成为理解朱熹认识论的ー个鲜明的新视角。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因为“格物致知”从根本上说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工夫论,而“全体大用”就是这ー工夫所要达到的境界。来自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朱人求教授,将话语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在《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一文中,朱人求从ー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审视朱子哲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对朱子全体大用观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朱人求指出隐藏在“全体大用”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在哲学层面,全体大用是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在社会实践层面,“全体大用”思想又落实在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等社会活动之中。从哲学层面到社会实践层面,全体大用思想显示出了从“心之全体大用”到“理”之“全体大用”的过渡,基本遵循了儒学从“德”到“治”,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此外,朱人求还指出,在“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中,后人对全体大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再生与变化。由此可见,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并不只是思维意识的认识活动,其以“全体大用”为境界指向,关乎着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成长。
纵观本次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着朱子学的前沿课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其观点之新颖,视角之多元,争论之激烈,都显示出朱子学全球化进程中的繁荣景象。朱子学不仅是东亚世界的思想财富,更是全球人民的文化瑰宝。本次会议不仅充分展示出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对于朱子学的全球化普及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ー、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
作为朱子学的核心,朱熹哲学是在朱熹与他人的反复论辩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在《朱陆之辩:朱熹时代的知识更新与辩论实践》一文中,来自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杜杰庸(Cuillaume Dutoumier )博士,强调了“论辩”在朱熹知识更新实践中的中心地位。杜杰庸从朱陆之辩切入,在研究了朱陆之辩的相关材料后,指明了隐藏在两位文人思想家关系背后的思想分化过程。杜杰庸认为,在朱陆之辩中,观念的相互作用暗示了一种文本的实用取向(a pragmatic approach ),基于此,杜杰庸试图坚持主位(emic )的观点,旨在形成对当时学术活动中论辩模式的更好理解。
作为ー套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哲学具有独特的哲学范畴与哲学问题。在《论朱子思想中人“心”之定位》一文中,来自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锦枝指出,朱子思想中的人“心”即不能说是“理”,也不能说是“气”,这种非理非气的定位使朱熹预先规避了心学可能产生的流弊,具有独特的价值。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金刚,着重分析了朱熹哲学中“气禀为何在源头上就有不齐”的问题。在《朱子论气运之不齐》一文中,赵金刚指出,万物之生并不是“ー齐生”,每个具体存在都有自己从创生到毁灭的过程。由是,不同的根据理而生、按照理而动的气之间便产生了摩擦,这样一来,动与静、主动与被动永恒地纠葛在ー起,无端无始,流行的气运之不齐也就因此产生。所以,朱子认为气运从源头上就有不齐,而这源头无它,即气之为气,气以理为根据而存在。朱子对理气的论述不仅实现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ー,也实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ー。
作为ー种东亚现象,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也独具特色,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哲学问题。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就对韩国大儒李栗谷的“人心道心”问题做了细致分疏。在《精微之境: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一文中,谢晓东指出,李栗谷对“人心”“道心”概念的界定具有两种主要视角:形上学视角和动机视角。在人心、道心的价值属性上,李栗谷始终如一地认为道心是纯善的,而对人心的价值属性判断则经历了从恶到不是恶再到有善有恶的演变。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上,李栗谷经历了从对立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到统ー论(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转变,其转变的关节点是1572年夏天栗谷与牛溪的论辩。谢晓东认为,李栗谷人心道心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两种善问题,即道心与人心之善是否为同一种善?解决这 ー理论困难的最佳方案有赖于回归朱 熹的人心通孔说。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财富,朱子学的当代研究也是生机盎然。在会上,德国波恩学者陈琦向我们介绍了德语区宋明理学的研究情况。陈琦指出,汉学大师福克(Alfred Forke ) 于1927〜1938年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德语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书中首次大量翻 译宋明理学经典的重要段落。福克将朱子学说分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四个部分,并视朱子为可以和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莱布尼茨相提并论的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此之后,德语地区陆续都有关于朱熹研究的专著出版,而21世纪的前十年在经典名著翻译与评注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此外,朱熹的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当代朱子学研究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会上,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汇报了《朱子语类》合刊本的编修计划。朱杰人指出,《徽州刊朱子语类》早于黎靖德的咸淳刻本,而作为《徽州刊朱子语类》的摹写本,《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简称“古写本”)区别于黎靖德咸淳刻本系统,而具有独立的文献价值。然而,学界却一直将古写本作为现存成化本[1]的校勘本,这不仅破坏了《徽州刊朱子语类》的原貌,而且也不能突出它存在的意义。因此,为了更直观全面地展示《朱子语类》的重要文献价值,将古写本与成化本编纂为《朱子语类》合刊本对世界朱子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朱子学与社会改革
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演绎着儒家哲学内圣外王的基本逻辑。在外王层面上,朱子学作为ー种文化现象,必然勾连着社会多方面的改革内容,而其中礼学更是对社会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胡秀娟博士在《朱熹和士庶通礼》一文中指出,朱熹的《家礼》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礼的应用已经从“礼不下庶人”转变成为“士庶通礼”。相较于司马光与程颐,朱熹《家礼》在冠、婚、丧、祭四方面对士庶通礼的损益内容,使得此后的礼仪与“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文化迥然有别。当然,朱熹并非一味注重从简从俗从众,他始终坚持对古礼进行适宜有度的去取折中,这对当时礼义亡阙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然而,来自中国浙江大学哲学系的衷鑫恣博士认为,道学实现的某些社会变革却反过来导致了道学为人所不喜甚或痛恨不绝如缕的现象。第一,道学将早期儒学的士人之教扩至士庶全体之教,这样一来,俗众普遍地视礼教为枷锁就会使道学大受敌意;第二,程朱以来,道学家之间好以讲学为事,风气相许,渐渐形成无形的道统集团,如此,势必被当权者所嫉,而终使政治与民间对道学的反对声汇流。
包括朱子礼学在内的宋代礼学,其特点之一便是注重“礼”之义理的阐发,这与汉代礼学注重“礼”之考据的学术风气迥然不同。正是由于这ー不同,清代礼学形成了汉宋之争。在《试析清儒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ーー以〈论语后案〉为例》一文中,中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肖永明和陈峰,将黄式三的《论语后案》视为清儒以“礼”解经的典范之作,并对其以“礼”解经的多重进路做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黄式三所著的《论语后案》以郑玄礼学为学问宗主,在重视三《礼》与《论语》互证的基础上以《周礼》为正。与仅以考证言“礼”的汉学家不同,黄式三更加注重礼意的建构,其治经既釆纳汉学所擅长的经史考证之学,同时也吸收宋学注重义理建构的长处,试图以礼学统摄汉宋学术,从而消泯门户之争。从肖永明和陈峰的文章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礼学似乎是中国文化的ー个ー贯之处。
朱子学不但对东亚各国的传统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朱子学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来自美国的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与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便在会上探讨了朱熹哲学与普世价值的问题。他们以《朱子家训》为中心,介绍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在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中推广《朱子家训》的历程,同时也分析了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与儒家学者对待普世价值的敌意态度。田浩与田梅指出,在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无须对讨论普世价值如此敏感和防卫,而西方亦应理解中国终会对“普世”做出调整或改变,将独特性融入普世性中,并可能影响全球。随着中国不断地权力集中化和提高全球地位,中国的学者和大众知识分子会继续受到政治统一和全球地位提升的影响。他们会重新注释普世宗教,亦会重新注释普世价值,这些“普世性”定会附上特定的中国痕迹和特点。
在朱熹哲学的成长过程中,以 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儒家一直是作为朱熹哲学的反对者而存在着的。德国波恩学者史克礼(Christian Schweirnann )在会上发表了《功利主义儒家的起源:荀子如何发现经济》一文,文章从田浩《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对陈亮功利主义的探讨岀发,将功利主义儒家的起源追溯到荀子。通过对《荀子•富国》的分析,史克礼指出,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以前,荀子就已提出劳动分工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协作是“上下俱富”的重要手段。在这里,荀子事实上是基于ー个分配正义的观念而提出了剩余财富的再分配。对于君王而言,荀子认为君王应当为了社会财富的流通而储存余粮且刺激经济,由此方能使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整个国家利益最大化。从史克礼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儒家的理论亦蕴含了对社会改革的诸多有益因素。
三、朱子学的认识论研究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是朱子学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它代表着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来自法国西巴黎大学的戴鹤白 (RogerDarrobers)指出,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原文的补注,是其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长期思考并提炼升华的结果。在回答门人有关“格物致知”问题的诸多答文中,朱熹为阐释《大学》中的知识起源论而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要素。在《朱熹对“理”这ー范畴的发展是认识论上的ー个进 步吗? ——从先秦儒家的“道”论出发评析》一文中,来自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杜仑认为,朱熹混淆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对主体自己,特别是主体的“伦理原则”认识的区别。除此之外,朱熹把道德观念形而上化为“理”,提出了认知和保存“理”的道心等概念,虽然继承发展了先秦的“知行观”,却不仅减低了天作为至上神在人类道德修养中的作用,而且也限制了人类在发展自己道德观念中的主动性。
事实上,对于朱熹“格物致 知”思想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在《诗歌视域下的朱熹认识论》 (Zhu Xi s Epistemology in Light of His
Foeり)一文中,来自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宇指出,朱熹留下的大量诗作对于更好地理解其格物致知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朱熹必须要面对那种以华丽辞藻描绘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自发情感的诗歌传统。此类诗歌因其所带有佛道的超越倾向,故与朱熹通过格物致知在此世寻“道”的认识论有所抵触。在朱熹与此类诗歌的斗争过程中,外在世界、内在情感和哲学倾向间的张力在朱熹的诗歌中被强化了,同时其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也更为集中和敏感,这便使得诗歌能够成为理解朱熹认识论的ー个鲜明的新视角。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因为“格物致知”从根本上说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工夫论,而“全体大用”就是这ー工夫所要达到的境界。来自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朱人求教授,将话语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在《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一文中,朱人求从ー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审视朱子哲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对朱子全体大用观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朱人求指出隐藏在“全体大用”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在哲学层面,全体大用是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在社会实践层面,“全体大用”思想又落实在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等社会活动之中。从哲学层面到社会实践层面,全体大用思想显示出了从“心之全体大用”到“理”之“全体大用”的过渡,基本遵循了儒学从“德”到“治”,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此外,朱人求还指出,在“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中,后人对全体大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再生与变化。由此可见,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并不只是思维意识的认识活动,其以“全体大用”为境界指向,关乎着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成长。
纵观本次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着朱子学的前沿课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其观点之新颖,视角之多元,争论之激烈,都显示出朱子学全球化进程中的繁荣景象。朱子学不仅是东亚世界的思想财富,更是全球人民的文化瑰宝。本次会议不仅充分展示出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对于朱子学的全球化普及亦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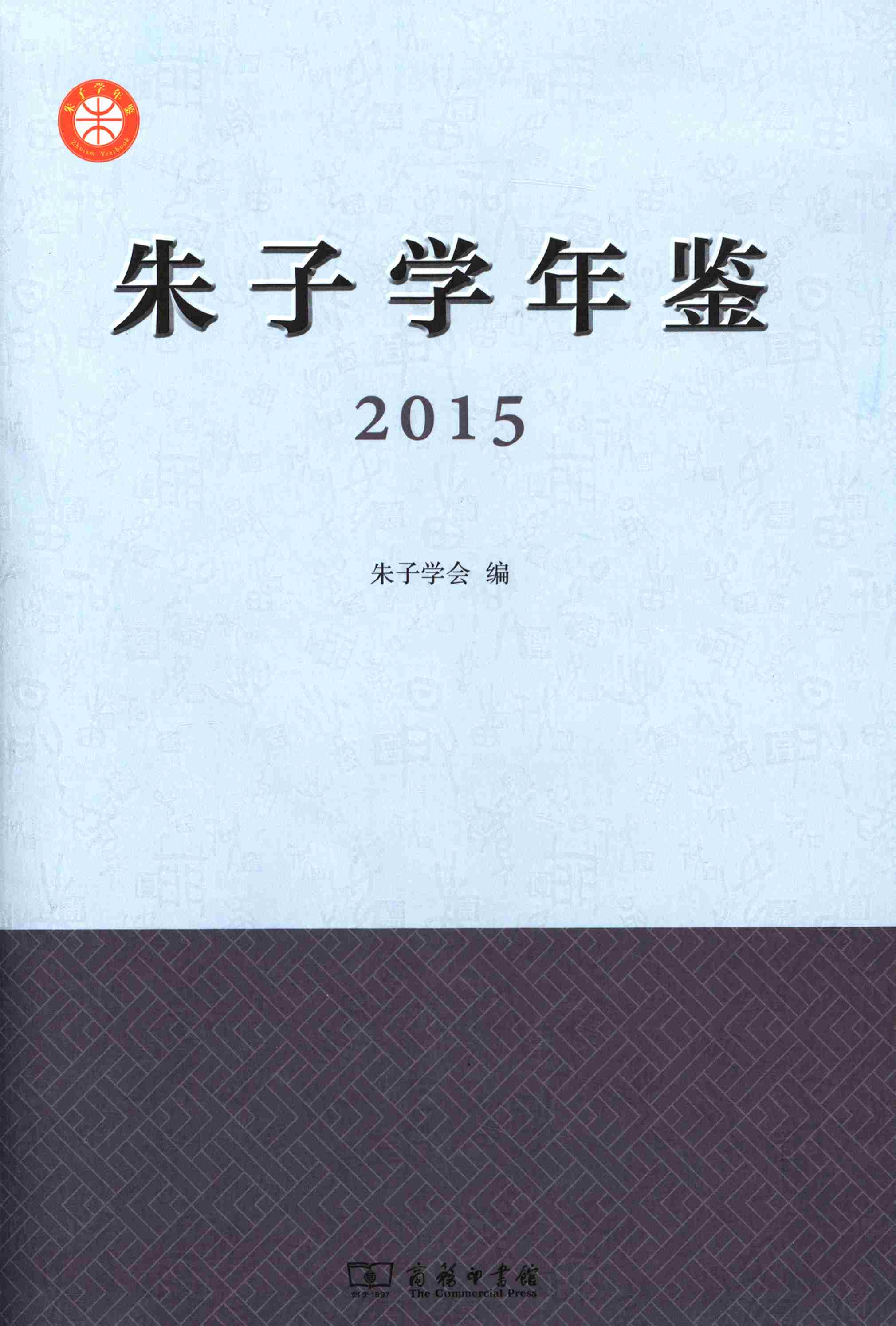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
相关人物
王凯立
责任者
相关事件
2015年7月11〜...
相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