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1]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15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1] |
| 其他题名: | 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82-9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包括“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等情况。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羽翼 辨正 |
内容
当朱子于“伪学”声中去世时,朱子学即身陷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在此情况下,以勉斋为首的朱门弟子以竭力弘扬朱子学为己任。在如何诠释朱子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弟子们虽因气质、学问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差异,但总体表现为以发明、维护朱子思想为宗旨。勉斋对朱子四书学的阐发,形成了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元诠释路向,奠定了诠释朱子四书学的基本样式,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勉斋学派,对“后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
勉斋认为,朱子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集注》,但该书精密简严,且与《精义》《或问》《文集》《语类》颇多分歧之处,必须对之展开再阐释,方能把握其旨意所在。《论语通释》即是勉斋对朱子《论语》的诠释之作。据《勉斋年谱》可知,该书为勉斋一生心血所在,成于其生命之终。勉斋以《通释》命名此书,是希望消除朱子论说之分歧,以定于一是。门人对此书给予了高度推崇,认为已将朱子《论语》疏通无遗。陈宓《题叙通释》说:“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2]《通释》对《集注》本旨的发明,主要采用以下方式:揭示《集注》用语、用意、针砭,辨析两说异同,以达到羽翼朱子的目的。
(一)用语、用意、学弊。《集注》用语“浑然如经”,须对之加以拆解式讲解,方能使其意义显明,利于理解。勉斋对《论语》学而章注的“善”和“复初”曾做了如下阐发:“‘明善’谓明天下之理,‘复其初’则复其本然之善也。”[3]很多情况下勉斋直接就《集注》“字义”逐字做出解释,如逐一解释温良恭俭让章“过化存神”四字。
如果说“用语”的解释是说明朱子说了什么,那么“用意”则要进一步揭示“用语”后面的用心所在。勉斋常以“何也”“故曰”等作为引语表示此意,仍以“学而”章注文阐发为例:“言君子而复归于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何也?学而至于成德,又岂有他道哉。”[4]
勉斋尤为留意存在多种诠释可能的文字,如《集注》解“伯夷叔齐”章“怨是用希”为“人亦不甚怨之也”。勉斋认为“怨”的施事主体可以是己、亦可是人,指出《集注》“人怨”解依据的是伯夷叔齐的圣贤境界。
《集注》特别重视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勉斋亦秉承此点。如《集注》为了激发学者修道进德之心,对接舆、沮、溺、丈人给予了高度肯定。勉斋以激昂之辞对四子做了高度赞扬,表达了对贪慕荣利之徒的痛恨。在“吾岂匏瓜”章亦指出,匏瓜是蠢然无知觉之物,人是万物之灵,应有所贡献于世界。世人借夫子此说为谋食四方辩护,丧失进退之义,背离了圣人本旨,必须加以辨正。“世之奔走以糊其口于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圣人之旨矣。”[5]
(二)两说异同。朱子四书学是以《集注》为核心的学术系统,但《集注》与《或问》《语类》等存在差异;《集注》所引二程学派之说与朱子思想存在差异;《集注》前后两解并存之异同值得留意;《集注》历经修改形成的前后差异之说,究竟何者为朱子定见,关乎朱子思想之把握。勉斋针对此四方面异同加以再诠释。
勉斋尤重视《集注》与《或问》的异同,《论孟集注》与《论孟或问》因写作时间、修改历程有别,彼此颇多差异。[6]勉斋对此多采取“两存之可也”的态度。如他指出见危致命章“《集注》以为‘庶乎其可’,则固恶其言之太快,然《或问》之意,则又与《集注》不同。读者两存之可也。”[7]《集注》认为“其可已矣”意在贬子张断语过于伤快,不够周全,但《或问》在比较“可也”与“其可已矣”时则认为前者贬抑,后者揄扬,《或问》说对学者仍有其价值,故当“两存之”。对《集注》与《语类》的不同,勉斋亦主张并存之。《集注》“三月不违”章注引“内外宾主之辨”说,《语类》对此有不同表述,勉斋从文义与义理双重角度给出两说并存的合理性。宾主说大概以屋子为喻,内主外宾,具体有两解:一是以仁为屋,心之出入往来为宾主。“其心三月不违仁”指心是否安于仁,更合乎文本义。二是以身为屋,仁之存亡为宾主,从文义言有所隔阂,但就义理言,此说心仁合一,心即是仁,心在即仁在,于为学工夫更紧切。
勉斋亦注意《或问》文义之误可能产生的义理偏差。如指出《或问》“切磋琢磨”的理解存在不当:
若谓“无谄无骄”为“如切如琢”,“乐与好礼”为“如磋如磨”,则下文“告往知来”一句便说不得。“切磋、琢磨”两句说得来也无精采……前之问答,盖言德之浅深;今之引《诗》,乃言学之疏密。[8]
《集注》指出切磋、琢磨是处理骨角、玉石的由粗到精的两项工序,切琢为粗,磋磨为精。勉斋认为,若将此粗精说直接对应于“无谄无骄”和“乐与好礼”,则会导致下文“告往知来”毫无着落,没有体现子贡的领悟与夫子的赞许,“切磋琢磨”说亦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和力量。此虽为微小文义差别,却不可放过。子贡师徒问答当与《诗》句讨论分开来看,分别指道德境界深浅和学问工夫疏密。
勉斋指出,《集注》引文与朱子注语总体应相互融洽、互为补足,“各有所发明也。”如“可与共学”章程、朱经权之说不同,勉斋认为,《集注》经权有别说使经、权意义分明而不至于混为一团;程子权变本质只是经说亦有道理,朱子所言对程子说具有补足、完善意义,“足以继此章之旨”。面对程、朱之异,包括勉斋在内的门人通常认为朱子解更好。如“祭如在”章,《集注》先引程子以孝敬释祭祀祖先神灵说,再补充己说。勉斋认为,祭祀根本在于真实无妄之诚意,朱子所补“诚意”恰补充了程子说之不足。勉斋有时直接指出程子说“不若《集注》之说为当”。如子夏之门人章的“先后”诠释,程子从教学次第立论,朱子就义理精粗而论,故朱子学更确。勉斋对朱子超越前人的推崇在关于仁的论述中表现得最鲜明,认为“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他在“仁而不佞”章说: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义,则仁之道无余蕴矣。……又断之曰“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深味“全体不息”四字,则学者而求至于仁,其至之标的,又昭然而可见矣。……其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大矣![9]
朱子孝悌为仁之本章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阐发仁的名义,透彻周全,可谓穷其底蕴而无余,本章则以“全体不息”四字昭然标示求仁之方。此四字极其精密含蓄地阐发了仁道及行仁之方,远迈前贤而有功于学者。且“全体”二字已囊括《集注》后章所引延平“当理无私心”之说,“不息”又进一步揭示其言外之意。
勉斋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对程、朱异同并非一味是朱非程,而是以自身判断为准,对朱子说同样有不少批评,有时亦认为“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如关于学而章解,他在《复叶味道书》中说:
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则是君子然后不愠。以悦、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
程子之说,方为稳当。[10]
《集注》所引程子说认为只有做到不愠方才是君子,朱子本人则认为只有成德君子方能做到不愠。据本章悦、乐、不愠三句文本的内在语义关系,程子说更恰当。其实,朱子说和程子说显然互补,勉斋从中看出朱子之不妥,颇出乎意外。
朱子就《集注》前后两说并存的情况有明确解释,认为这是因两说皆有可取,无法舍弃,但前说要优于后说。勉斋据贴切文义和为学工夫的原则对之有所辨析。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忍”,《集注》有忍心、容忍前后两义,但所选范氏说为容忍义、谢氏说为忍心义,这样就使得本应在后的范氏容忍义反而在前。勉斋的解答是:范氏、谢氏论域不同,前者就全章而发,后者仅针对“是可忍”而论。又如人而不仁章《集注》先后引游酢、程子说。游氏以人心解仁,较程子以正理解仁更亲切。朱子同时选用二说,表明仁应当包含人心与正理的统一。在勉斋看来,心与仁的关系更为紧密。
《集注》初本与改本是朱子后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出朱子思想的演变,对准确把握朱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亦能考验学者对朱子思想的把握能力。勉斋指出“博学笃志”章存在初本和改本之别:前者“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过于分析,带有有所为而外求的弊病,后者“所存自熟”则纯从心之存主立论,专注于内心的操存涵养,进一步突出了心与仁的内在一体性,显示出《集注》修改之精密。
《集注》初本谓“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后乃以“所存自熟”易之。
盖初本以博笃切近为“心不外驰”,学志问思为“事皆有益”。其后易之者,则专主于“心之所存”而言也。……以此见《集注》愈改而愈精也。[11]
二、“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勉斋于朱子兼具女婿与弟子双重身份,深知朱子四书诠释用心之勤,故再三告诫学者对《集注》切不可抱轻易之心。出乎意料的是,勉斋在《论语》诠释中,对《集注》却不大客气地给予批评。《复叶味道书》集中表达了他对《集注》的修正看法:
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朱先生云:“敏于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此用《中庸》“有余不敢尽”之语,然所谓“慎”者,非以其有余而慎之也。“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事难行故当勉,言易肆故当慎耳。人而无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当用“其何以观”例。“志道、据德、依仁”不当作次第说,若作次第说,则“游艺”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据德、据德者未能依仁之病。……德则行道而有得于身,随其所得,守之而不失。[12
勉斋指出,不应为了保持统一而删除《语录》不同之说。朱子对二程语录的处理,亦是尽量保持原貌。天下义理无穷,并不能保证编者所见为的当之
论。即便朱子穷毕生精力所注之《论语》,亦多有不满人意处,这恰可以借《语录》之说看出,《语录》异说具有参考、矫正《集注》的价值。他举出《集注》中四处错误,从文义、义理、工夫上加以批评:学而章朱子解不如程子说精当;以《中庸》“有余不敢尽”解释“慎于言”不妥,慎只是谨慎勉励,并无有余义;“何以行之”的“以”解为“能够”不对,当解为“居上不宽”章的“凭借”义;志道章《集注》《语录》皆反复言及四者先后次序不可乱、本末精粗必有序,这一视四者为造道次第的观点,不仅导致“游于艺”无所安置,且割裂了志道、据德、依仁与人的关联,学者对道、德、仁皆需要始终用力而不可有须臾放弃,四者在价值序列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它们是并列而非次第关系。在文义上,勉斋还质疑《集注》博文约礼章的“约,要也”说,认为此处约之于礼的“约”显然为动词,是“约之”义,训为“要”不合文理。如训为“约束”,虽合乎文义,却未能突出与“博”的对举义,当合二者而取之,为“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其实质不过是存心而已。勉斋有时会通过否定《集注》所引说来间接表达批评。如“君子九思”章《集注》引程子“九思各专其一”说,勉斋认为专一而思的弊病是泛泛而思却毫无统绪、效果,思应当建立在戒慎敬义的基础上。
历来对十五志学章的理解,存在一个困惑:夫子所言自十五有志至于七十不逾矩的修道历程当如何观之?是开示真实语还是示教象征语?《集注》引程子说,认为“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朱子自评为,“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认为夫子生知之圣,其进道修得次序未必循此阶梯而进,未必有如此明确的渐进过程。但圣人并不自以为是,其说乃为学者展示为学上升之次第,是夫子修道进程的大略标示,希望学者据此为准则而加以对照自勉,并非是夫子内心自以为已达到了圣人境界而托之以此谦虚推脱之辞。故此说虽为夫子的一种谦辞,但此谦辞仍有其真实内容所在。勉斋对此提出了批判性看法:
圣人生知安行,有见夫义理之在人,不啻如饥食渴饮之急,则夫知而必学,学而必好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十年十五年而后一进,亦圣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说者以为圣人立法谦辞以勉人,则圣人皆是架空虚诞之辞,岂圣人正大之心哉!故《集注》虽以勉人为辞而又以独觉其进为说,亦可见矣。[13]
所谓圣人生知安行乃是指知义理之深,学义理之笃,好义理之切,是对学的知之、好之、乐之,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所在。圣人与常人的区别不是从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成就论,而是就其对义理之学的学习态度、能力论。至于十年、十五年的进学层次,则是圣人之学达到某一层次自信的表现,是见之真、行之切的真实自得的流露,并非是圣人为了勉励学者、为学者立法的谦辞。《集注》尽管主张这是圣人之勉辞,但同时又提出是圣人“独觉其进”处。其实,《集注》更强调勉人、立法、谦虚之说,“独觉其进”说不过略有此意而已。勉斋则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以此作为对《集注》的批评修正。
朱子《集注》之修改完善,是在与弟子讲学辩难中展开的。朱子善于包容、吸取意见的学风培育了弟子勇于质疑的学术品格。勉斋尤其保持了这种学风,故对《集注》时加质疑,体现出唯理是从的精神,勇于批判亦成为勉斋学派的一大特色。如传勉斋学的江西一派,以“多不同于朱子”的饶双峰为代表,其对朱子四书义理有着精细辩难,涉及格物传、忠恕解、心性论等核心论题,如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说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指出以朱子之高明、精密,对程子说的理解仍然存在重要差失,可见质疑问难之必要。“《集注》主一而废一,所以于曾子用工处,又别说从一路去。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14]勉斋所传于浙江的北山学派亦秉承此种怀疑批判精神,如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从考据学入手,对《集注》文字音韵训诂等颇多补正。
三、“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
勉斋据当时学术情况,有意彰显了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较之讲学穷理,“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才是工夫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论的内转。
“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勉斋体现出重“心”的立场,视心为万化根本,人身主宰,具有参赞天地之化育,修齐治平之效用,批评世人对心有所轻视。“心者,天地之蕴,化育之机……甚矣,人之轻视其心也。”[15]他于礼云章、人而不仁章辨别《集注》二说优劣时,皆强调心对于理的优先性,事理必须安顿在人心上才有意义,若无心为据依之地,则理是寡头无根的。并于《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中提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的心性为一论,发朱子所未发。说:“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仁义礼智皆具于心,而谓‘心在性外’,可乎?至于为说,则曰‘心出于性’,何其与孟子之言相戾乎?……则此心之妙,但有虚明而无礼义矣。”[16]批评黄子洪的心在性外、心出于性说割裂了心性关系,作为性之内容的五常皆根于心,故性在心内,“心出于性”则导致心丧失了义理内涵,仅仅成为知觉虚明之心。在“明德”的讨论中他亦主张心即性、性即心的心性为一说。《复杨志仁书》说:
此但当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今观所答,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
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则仁又便是心。《大学》所解明德,则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17]
解答明德究竟是性是心的疑问,应从心性为一的角度着眼,批评杨志仁说导致心性为二。心与仁具有分合关系,既有各自为二,不可合一的情况,如颜子三月不违仁;亦有心即是仁的合一情况,如孟子仁人心说。“明德”则是心性即一的概念。勉斋特别突出了“心即仁也”这一心与仁相合的向度,在分析仁的内外宾主之辨即提出“以义理言,则心即仁也。……其旨尤切”。弟子双峰指出孟子“仁人心”与“求放心”之心皆应指义理之心,批评《集注》从知觉之心理解“求放心”,与“仁人心”说不相应。勉斋认同双峰说,提出心有义理、知觉两面,其中又存在专指一面和合指两面的情况,故心性之分合说需具体分析,“心字有专指知觉一边而言者,有专指义理一边而言者,有合知觉义理而为言者。须逐处看得分晓”。勉斋还提出“非性情之外别有心”说[18],意在强调心与性情并非为二,心就是性情,是性情中对之起主宰作用者。
勉斋指出,重章句与重存养的朱陆两家工夫主导学界,二者“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各有优劣。在一般意义上,勉斋主张讲学、存养不可偏废,此即朱子合尊德性、道问学为一的立场。《复饶伯舆》言,“守章句者不知存养之为切,谈存养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缓,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卒无得焉”[19]。但因药发病、矫正学弊是决定勉斋工夫立场的关键因素,有见于朱子学者易于偏向章句讲学,缺乏身心存养,勉斋反复呼吁学者工夫当从以讲学穷理为主转移到身心上来。存养决定了致知之效,无存养,致知将流入讲说文字的口耳之学而毫无益处,说“须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论辞章,恐终不济事也”[20]。
“检点身心”。勉斋反复论及学问根本就是治心修身。“学问之道,治心修身而已。”在给双峰信中指出,古人之学在身心用功,以检点身心为主,讲学穷理为辅。透过格物穷理与检点身心工夫的对比,突出检点身心工夫的主导地位。《复饶伯舆》言:
近亦颇觉古人为学,大抵先于身心上用功……无非欲人检点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故初学之法,且令格物穷理……亦卒归于检点身心而
已。年来学者,但见古人有格物穷理之说,但驰心于辨析讲论之间,而不务持养省察之实……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寻行数墨,入耳出口,以为即此便是学问,……则虽曰学者之众,而适足以为吾道之累也。[21]
就往古圣贤用功之语来看,如尧舜精一之传、文王心事之制等,皆是检点身心工夫。钻研圣贤经典的格物穷理之功,是为了探究为学之方、获得正确义理,以做到居敬集义,最终归于检点身心。检点身心是格物穷理的目标所在。为此,勉斋严厉斥责学者放荡身心,埋头义理辨析之中,丧失了操存涵养自我反省的身心工夫,流于言行背离的口耳之学,走向了圣人之教的背面。痛切指出,讲学穷理人数虽众,却不仅无益于道之传承,反而会伤害之。强调检点身心而非格物穷理,才是道之传承的根本所在。为此,他强调持养省察工夫与讲学穷理的区别,批评饶鲁将二者合说有误。
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皆务外者也。……居敬集义乃是要检点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晓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
可合而言之也。
既然圣贤教人工夫皆是检点身心,故学者为学用心,自当以持养省察、敬义夹持工夫为主,讲学穷理乃辅助涵养省察工夫者,为学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仅仅追求讲学穷理,则是向外为人之学,而非切己向内之学。敬义工夫要求在念头思虑上用功,通过持养、省察双向并进之方,达到内直外方之效用。敬义是检点身心的实践工夫,格致是探究事理工夫,二者所主不同,应严格区分而不可混为一体。在与李燔的信中,他亦将检点身心与讲学穷理对立起来,痛斥流于讲学是儒道失传的罪魁祸首,强烈表达了应以身心点检为主的思想。《与李敬子司直书》言:
近读《中庸》,因推考古先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博文易而约礼难。后来学者专务其所易而常惮其所难,此道之所以无传……若
但务学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学问也。……独南康德契兄与诸贤维持,讲学最盛……但不知于身心上点检处如何耳。[22]
古代圣贤之学皆是就身心用工,如《书》之人心道心、《易》之直内方外,皆是论身心工夫而非讲学。夫子担心学者认识倾向一偏,故以博文与约礼对举,希望兼顾讲学之文与实践之礼。就先后论,博文在约礼之前;就难易论,约礼更甚于博文,而学者流于外在讲学而放弃了约礼工夫,直接导致道的失传。当以戒惧慎独工夫为补救之方,以之为毕生事业而时刻遵循,讲学穷理不过起讲明戒慎的辅助作用。如仅知讲学则丧失了学问根本,学问根本在于身心实践。南康虽然为目下师门讲学最盛之地,更应用功于身心检点。
勉斋反复指出检点身心的意义,以极为强烈的对比性措辞强调是否有检点工夫是人生分界所在。“不到此间议论,虽杀人放火,自不相干;既到此间议论,须是检点自己,从头到尾,得彻方是。”[23]晚年屡屡道及检点身心是人生唯一重要之事,百事皆当放下,唯独检点身心工夫不可丝毫放松。“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检点身心为急也。”[24]只有检点身心才能使人性光明、纯粹、洁净如初,而恢复本初,不负此生。“今亦他无所用心,只得检点身心,令明净纯洁,交还天地父母耳。”[25]
勉斋非常重视孟子的“求放心”说,认为此是极重要的身心工夫,提出“存心之学”与辞章记问之学的区别。人心受到物欲拖累,就会放荡奔跑,从而丧失天理之约束,故圣贤以战战兢兢的静存动察工夫,来确保本心的存在。孟子求放心说是对学者提出的真切警诫,事关儒家之道的传承,秦汉以来学者沉溺于辞章、记问之学而丧失了古人存心、求心之学,直到周程先生,方才接续道统。学者于动静寝食中,皆当时刻牢记“求放心”而不可须臾偏离之,此为读书穷理之根本。“且是以‘求放心’为本,一动一静、一寝一食,不可离此三字,便有以为之根本,然后可以读书玩理也。”[26]多次告诫学者读朱先生书,应加倍于求放心工夫,反复批评过于思索文义的行为。强调自家心灵是书本文义的主宰,不能以书本之说漫过身心,提出“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说,此与象山“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说精神颇有相通。并多方设法,诱导学者反归于求放心。
先生曰:“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可也。”又尝言,“学者役精神于文义而不反求诸心,终未免有口耳之学。”故于讲论之际,必宛转而归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27]
勉斋亦强调存念头的重要。指出作为工夫之首的戒惧,具有自然、简易、内在、当下的特点,一念即是,不待他求,不待外索。直接将之简化为当下一念,这与心学的当下说相通。《复黄会卿》言,“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28]如能存心,则念头存而不失的当下,万理皆在。“存心则一念存,万理具”。帝王之学亦不过是通过检束、防制其心,使念头皆合乎中道。穷理玩索工夫未能专注精一,原因在于“反身一念”未能做到。而贤愚之分的关键亦在于为学念头是在身心之内还是在其之外。
勉斋尽管凸显了心的本体义,推崇反身向内的“求心”工夫,但并未走向象山“心学”,而是坚持并发展了朱子学的主敬立场。为学首要是检点身心而非读书,检点身心之首则是持敬。“为学须先理会心,理会心先须持敬。”[29]主敬不仅是求放心之要旨,更是必须牢记于心、须臾不可离的“护身符”,是学者为学的必备之方,是儒家抗拒一切鬼魔上身的救命符。“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便是护身符。”[30]
勉斋身心内转之学,得到后人的继承认可。吴昌裔指出,勉斋以居敬集义为主的身心点检向内工夫,是对文公之学的进一步推阐。“先生体贴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是则文公有功于程氏,而先生有助于师门。”[31]勉斋“内转”之学在弟子双峰那里得到弘扬。除批评朱子“求放心”章对“心”的理解析为义理与知觉外,在牛山之木章双峰又提出同样的批评。双峰之学体现出追求合一、简易之学的特点,多处批评朱子之解过于分析,如批评朱子将“诚”与“道”析为“本、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等说过于支离;以知行交互解三达德又“头绪未免太多”等。
朱陆异同是朱子后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北溪表现出极力捍卫师门、抨击象山的态度,勉斋对陆学态度相对温和,认为其最大问题是“不读书”,但勉斋自身对读书的态度又颇矛盾,认为只是第二义,第一义是持敬收心,批评“后生辈皆以为读书者,充塞时文之具矣”[32]。双峰虽亦不满于象山不读书说,却提出“尊德性以为之本”说。如何看待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判定朱陆学者立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双峰后学的吴澄则更因力倡“尊德性为本”而被视为陆学,成为元代朱陆合流的代表。其中虽不无误解,但自朱子格物穷理到勉斋“点检身心”再至双峰、草庐“尊德性为本”,确乎显示出“后朱子学”演变的某种真实轨迹和趋向。
勉斋《论语》诠释,体现出对朱子学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重趋向,奠定了“后朱子学”经典诠释的基本样式,弘扬了朱子学的理性辨正精神,指引了朱子学转向内在身心的工夫路线,昭示了日后朱陆异同话题的彰显,对深入研究朱子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一、“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
勉斋认为,朱子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集注》,但该书精密简严,且与《精义》《或问》《文集》《语类》颇多分歧之处,必须对之展开再阐释,方能把握其旨意所在。《论语通释》即是勉斋对朱子《论语》的诠释之作。据《勉斋年谱》可知,该书为勉斋一生心血所在,成于其生命之终。勉斋以《通释》命名此书,是希望消除朱子论说之分歧,以定于一是。门人对此书给予了高度推崇,认为已将朱子《论语》疏通无遗。陈宓《题叙通释》说:“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2]《通释》对《集注》本旨的发明,主要采用以下方式:揭示《集注》用语、用意、针砭,辨析两说异同,以达到羽翼朱子的目的。
(一)用语、用意、学弊。《集注》用语“浑然如经”,须对之加以拆解式讲解,方能使其意义显明,利于理解。勉斋对《论语》学而章注的“善”和“复初”曾做了如下阐发:“‘明善’谓明天下之理,‘复其初’则复其本然之善也。”[3]很多情况下勉斋直接就《集注》“字义”逐字做出解释,如逐一解释温良恭俭让章“过化存神”四字。
如果说“用语”的解释是说明朱子说了什么,那么“用意”则要进一步揭示“用语”后面的用心所在。勉斋常以“何也”“故曰”等作为引语表示此意,仍以“学而”章注文阐发为例:“言君子而复归于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何也?学而至于成德,又岂有他道哉。”[4]
勉斋尤为留意存在多种诠释可能的文字,如《集注》解“伯夷叔齐”章“怨是用希”为“人亦不甚怨之也”。勉斋认为“怨”的施事主体可以是己、亦可是人,指出《集注》“人怨”解依据的是伯夷叔齐的圣贤境界。
《集注》特别重视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勉斋亦秉承此点。如《集注》为了激发学者修道进德之心,对接舆、沮、溺、丈人给予了高度肯定。勉斋以激昂之辞对四子做了高度赞扬,表达了对贪慕荣利之徒的痛恨。在“吾岂匏瓜”章亦指出,匏瓜是蠢然无知觉之物,人是万物之灵,应有所贡献于世界。世人借夫子此说为谋食四方辩护,丧失进退之义,背离了圣人本旨,必须加以辨正。“世之奔走以糊其口于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圣人之旨矣。”[5]
(二)两说异同。朱子四书学是以《集注》为核心的学术系统,但《集注》与《或问》《语类》等存在差异;《集注》所引二程学派之说与朱子思想存在差异;《集注》前后两解并存之异同值得留意;《集注》历经修改形成的前后差异之说,究竟何者为朱子定见,关乎朱子思想之把握。勉斋针对此四方面异同加以再诠释。
勉斋尤重视《集注》与《或问》的异同,《论孟集注》与《论孟或问》因写作时间、修改历程有别,彼此颇多差异。[6]勉斋对此多采取“两存之可也”的态度。如他指出见危致命章“《集注》以为‘庶乎其可’,则固恶其言之太快,然《或问》之意,则又与《集注》不同。读者两存之可也。”[7]《集注》认为“其可已矣”意在贬子张断语过于伤快,不够周全,但《或问》在比较“可也”与“其可已矣”时则认为前者贬抑,后者揄扬,《或问》说对学者仍有其价值,故当“两存之”。对《集注》与《语类》的不同,勉斋亦主张并存之。《集注》“三月不违”章注引“内外宾主之辨”说,《语类》对此有不同表述,勉斋从文义与义理双重角度给出两说并存的合理性。宾主说大概以屋子为喻,内主外宾,具体有两解:一是以仁为屋,心之出入往来为宾主。“其心三月不违仁”指心是否安于仁,更合乎文本义。二是以身为屋,仁之存亡为宾主,从文义言有所隔阂,但就义理言,此说心仁合一,心即是仁,心在即仁在,于为学工夫更紧切。
勉斋亦注意《或问》文义之误可能产生的义理偏差。如指出《或问》“切磋琢磨”的理解存在不当:
若谓“无谄无骄”为“如切如琢”,“乐与好礼”为“如磋如磨”,则下文“告往知来”一句便说不得。“切磋、琢磨”两句说得来也无精采……前之问答,盖言德之浅深;今之引《诗》,乃言学之疏密。[8]
《集注》指出切磋、琢磨是处理骨角、玉石的由粗到精的两项工序,切琢为粗,磋磨为精。勉斋认为,若将此粗精说直接对应于“无谄无骄”和“乐与好礼”,则会导致下文“告往知来”毫无着落,没有体现子贡的领悟与夫子的赞许,“切磋琢磨”说亦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和力量。此虽为微小文义差别,却不可放过。子贡师徒问答当与《诗》句讨论分开来看,分别指道德境界深浅和学问工夫疏密。
勉斋指出,《集注》引文与朱子注语总体应相互融洽、互为补足,“各有所发明也。”如“可与共学”章程、朱经权之说不同,勉斋认为,《集注》经权有别说使经、权意义分明而不至于混为一团;程子权变本质只是经说亦有道理,朱子所言对程子说具有补足、完善意义,“足以继此章之旨”。面对程、朱之异,包括勉斋在内的门人通常认为朱子解更好。如“祭如在”章,《集注》先引程子以孝敬释祭祀祖先神灵说,再补充己说。勉斋认为,祭祀根本在于真实无妄之诚意,朱子所补“诚意”恰补充了程子说之不足。勉斋有时直接指出程子说“不若《集注》之说为当”。如子夏之门人章的“先后”诠释,程子从教学次第立论,朱子就义理精粗而论,故朱子学更确。勉斋对朱子超越前人的推崇在关于仁的论述中表现得最鲜明,认为“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他在“仁而不佞”章说: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义,则仁之道无余蕴矣。……又断之曰“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深味“全体不息”四字,则学者而求至于仁,其至之标的,又昭然而可见矣。……其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大矣![9]
朱子孝悌为仁之本章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阐发仁的名义,透彻周全,可谓穷其底蕴而无余,本章则以“全体不息”四字昭然标示求仁之方。此四字极其精密含蓄地阐发了仁道及行仁之方,远迈前贤而有功于学者。且“全体”二字已囊括《集注》后章所引延平“当理无私心”之说,“不息”又进一步揭示其言外之意。
勉斋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对程、朱异同并非一味是朱非程,而是以自身判断为准,对朱子说同样有不少批评,有时亦认为“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如关于学而章解,他在《复叶味道书》中说:
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则是君子然后不愠。以悦、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
程子之说,方为稳当。[10]
《集注》所引程子说认为只有做到不愠方才是君子,朱子本人则认为只有成德君子方能做到不愠。据本章悦、乐、不愠三句文本的内在语义关系,程子说更恰当。其实,朱子说和程子说显然互补,勉斋从中看出朱子之不妥,颇出乎意外。
朱子就《集注》前后两说并存的情况有明确解释,认为这是因两说皆有可取,无法舍弃,但前说要优于后说。勉斋据贴切文义和为学工夫的原则对之有所辨析。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忍”,《集注》有忍心、容忍前后两义,但所选范氏说为容忍义、谢氏说为忍心义,这样就使得本应在后的范氏容忍义反而在前。勉斋的解答是:范氏、谢氏论域不同,前者就全章而发,后者仅针对“是可忍”而论。又如人而不仁章《集注》先后引游酢、程子说。游氏以人心解仁,较程子以正理解仁更亲切。朱子同时选用二说,表明仁应当包含人心与正理的统一。在勉斋看来,心与仁的关系更为紧密。
《集注》初本与改本是朱子后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出朱子思想的演变,对准确把握朱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亦能考验学者对朱子思想的把握能力。勉斋指出“博学笃志”章存在初本和改本之别:前者“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过于分析,带有有所为而外求的弊病,后者“所存自熟”则纯从心之存主立论,专注于内心的操存涵养,进一步突出了心与仁的内在一体性,显示出《集注》修改之精密。
《集注》初本谓“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后乃以“所存自熟”易之。
盖初本以博笃切近为“心不外驰”,学志问思为“事皆有益”。其后易之者,则专主于“心之所存”而言也。……以此见《集注》愈改而愈精也。[11]
二、“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勉斋于朱子兼具女婿与弟子双重身份,深知朱子四书诠释用心之勤,故再三告诫学者对《集注》切不可抱轻易之心。出乎意料的是,勉斋在《论语》诠释中,对《集注》却不大客气地给予批评。《复叶味道书》集中表达了他对《集注》的修正看法:
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朱先生云:“敏于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此用《中庸》“有余不敢尽”之语,然所谓“慎”者,非以其有余而慎之也。“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事难行故当勉,言易肆故当慎耳。人而无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当用“其何以观”例。“志道、据德、依仁”不当作次第说,若作次第说,则“游艺”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据德、据德者未能依仁之病。……德则行道而有得于身,随其所得,守之而不失。[12
勉斋指出,不应为了保持统一而删除《语录》不同之说。朱子对二程语录的处理,亦是尽量保持原貌。天下义理无穷,并不能保证编者所见为的当之
论。即便朱子穷毕生精力所注之《论语》,亦多有不满人意处,这恰可以借《语录》之说看出,《语录》异说具有参考、矫正《集注》的价值。他举出《集注》中四处错误,从文义、义理、工夫上加以批评:学而章朱子解不如程子说精当;以《中庸》“有余不敢尽”解释“慎于言”不妥,慎只是谨慎勉励,并无有余义;“何以行之”的“以”解为“能够”不对,当解为“居上不宽”章的“凭借”义;志道章《集注》《语录》皆反复言及四者先后次序不可乱、本末精粗必有序,这一视四者为造道次第的观点,不仅导致“游于艺”无所安置,且割裂了志道、据德、依仁与人的关联,学者对道、德、仁皆需要始终用力而不可有须臾放弃,四者在价值序列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它们是并列而非次第关系。在文义上,勉斋还质疑《集注》博文约礼章的“约,要也”说,认为此处约之于礼的“约”显然为动词,是“约之”义,训为“要”不合文理。如训为“约束”,虽合乎文义,却未能突出与“博”的对举义,当合二者而取之,为“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其实质不过是存心而已。勉斋有时会通过否定《集注》所引说来间接表达批评。如“君子九思”章《集注》引程子“九思各专其一”说,勉斋认为专一而思的弊病是泛泛而思却毫无统绪、效果,思应当建立在戒慎敬义的基础上。
历来对十五志学章的理解,存在一个困惑:夫子所言自十五有志至于七十不逾矩的修道历程当如何观之?是开示真实语还是示教象征语?《集注》引程子说,认为“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朱子自评为,“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认为夫子生知之圣,其进道修得次序未必循此阶梯而进,未必有如此明确的渐进过程。但圣人并不自以为是,其说乃为学者展示为学上升之次第,是夫子修道进程的大略标示,希望学者据此为准则而加以对照自勉,并非是夫子内心自以为已达到了圣人境界而托之以此谦虚推脱之辞。故此说虽为夫子的一种谦辞,但此谦辞仍有其真实内容所在。勉斋对此提出了批判性看法:
圣人生知安行,有见夫义理之在人,不啻如饥食渴饮之急,则夫知而必学,学而必好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十年十五年而后一进,亦圣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说者以为圣人立法谦辞以勉人,则圣人皆是架空虚诞之辞,岂圣人正大之心哉!故《集注》虽以勉人为辞而又以独觉其进为说,亦可见矣。[13]
所谓圣人生知安行乃是指知义理之深,学义理之笃,好义理之切,是对学的知之、好之、乐之,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所在。圣人与常人的区别不是从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成就论,而是就其对义理之学的学习态度、能力论。至于十年、十五年的进学层次,则是圣人之学达到某一层次自信的表现,是见之真、行之切的真实自得的流露,并非是圣人为了勉励学者、为学者立法的谦辞。《集注》尽管主张这是圣人之勉辞,但同时又提出是圣人“独觉其进”处。其实,《集注》更强调勉人、立法、谦虚之说,“独觉其进”说不过略有此意而已。勉斋则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以此作为对《集注》的批评修正。
朱子《集注》之修改完善,是在与弟子讲学辩难中展开的。朱子善于包容、吸取意见的学风培育了弟子勇于质疑的学术品格。勉斋尤其保持了这种学风,故对《集注》时加质疑,体现出唯理是从的精神,勇于批判亦成为勉斋学派的一大特色。如传勉斋学的江西一派,以“多不同于朱子”的饶双峰为代表,其对朱子四书义理有着精细辩难,涉及格物传、忠恕解、心性论等核心论题,如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说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指出以朱子之高明、精密,对程子说的理解仍然存在重要差失,可见质疑问难之必要。“《集注》主一而废一,所以于曾子用工处,又别说从一路去。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14]勉斋所传于浙江的北山学派亦秉承此种怀疑批判精神,如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从考据学入手,对《集注》文字音韵训诂等颇多补正。
三、“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
勉斋据当时学术情况,有意彰显了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较之讲学穷理,“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才是工夫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论的内转。
“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勉斋体现出重“心”的立场,视心为万化根本,人身主宰,具有参赞天地之化育,修齐治平之效用,批评世人对心有所轻视。“心者,天地之蕴,化育之机……甚矣,人之轻视其心也。”[15]他于礼云章、人而不仁章辨别《集注》二说优劣时,皆强调心对于理的优先性,事理必须安顿在人心上才有意义,若无心为据依之地,则理是寡头无根的。并于《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中提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的心性为一论,发朱子所未发。说:“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仁义礼智皆具于心,而谓‘心在性外’,可乎?至于为说,则曰‘心出于性’,何其与孟子之言相戾乎?……则此心之妙,但有虚明而无礼义矣。”[16]批评黄子洪的心在性外、心出于性说割裂了心性关系,作为性之内容的五常皆根于心,故性在心内,“心出于性”则导致心丧失了义理内涵,仅仅成为知觉虚明之心。在“明德”的讨论中他亦主张心即性、性即心的心性为一说。《复杨志仁书》说:
此但当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今观所答,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
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则仁又便是心。《大学》所解明德,则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17]
解答明德究竟是性是心的疑问,应从心性为一的角度着眼,批评杨志仁说导致心性为二。心与仁具有分合关系,既有各自为二,不可合一的情况,如颜子三月不违仁;亦有心即是仁的合一情况,如孟子仁人心说。“明德”则是心性即一的概念。勉斋特别突出了“心即仁也”这一心与仁相合的向度,在分析仁的内外宾主之辨即提出“以义理言,则心即仁也。……其旨尤切”。弟子双峰指出孟子“仁人心”与“求放心”之心皆应指义理之心,批评《集注》从知觉之心理解“求放心”,与“仁人心”说不相应。勉斋认同双峰说,提出心有义理、知觉两面,其中又存在专指一面和合指两面的情况,故心性之分合说需具体分析,“心字有专指知觉一边而言者,有专指义理一边而言者,有合知觉义理而为言者。须逐处看得分晓”。勉斋还提出“非性情之外别有心”说[18],意在强调心与性情并非为二,心就是性情,是性情中对之起主宰作用者。
勉斋指出,重章句与重存养的朱陆两家工夫主导学界,二者“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各有优劣。在一般意义上,勉斋主张讲学、存养不可偏废,此即朱子合尊德性、道问学为一的立场。《复饶伯舆》言,“守章句者不知存养之为切,谈存养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缓,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卒无得焉”[19]。但因药发病、矫正学弊是决定勉斋工夫立场的关键因素,有见于朱子学者易于偏向章句讲学,缺乏身心存养,勉斋反复呼吁学者工夫当从以讲学穷理为主转移到身心上来。存养决定了致知之效,无存养,致知将流入讲说文字的口耳之学而毫无益处,说“须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论辞章,恐终不济事也”[20]。
“检点身心”。勉斋反复论及学问根本就是治心修身。“学问之道,治心修身而已。”在给双峰信中指出,古人之学在身心用功,以检点身心为主,讲学穷理为辅。透过格物穷理与检点身心工夫的对比,突出检点身心工夫的主导地位。《复饶伯舆》言:
近亦颇觉古人为学,大抵先于身心上用功……无非欲人检点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故初学之法,且令格物穷理……亦卒归于检点身心而
已。年来学者,但见古人有格物穷理之说,但驰心于辨析讲论之间,而不务持养省察之实……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寻行数墨,入耳出口,以为即此便是学问,……则虽曰学者之众,而适足以为吾道之累也。[21]
就往古圣贤用功之语来看,如尧舜精一之传、文王心事之制等,皆是检点身心工夫。钻研圣贤经典的格物穷理之功,是为了探究为学之方、获得正确义理,以做到居敬集义,最终归于检点身心。检点身心是格物穷理的目标所在。为此,勉斋严厉斥责学者放荡身心,埋头义理辨析之中,丧失了操存涵养自我反省的身心工夫,流于言行背离的口耳之学,走向了圣人之教的背面。痛切指出,讲学穷理人数虽众,却不仅无益于道之传承,反而会伤害之。强调检点身心而非格物穷理,才是道之传承的根本所在。为此,他强调持养省察工夫与讲学穷理的区别,批评饶鲁将二者合说有误。
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皆务外者也。……居敬集义乃是要检点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晓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
可合而言之也。
既然圣贤教人工夫皆是检点身心,故学者为学用心,自当以持养省察、敬义夹持工夫为主,讲学穷理乃辅助涵养省察工夫者,为学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仅仅追求讲学穷理,则是向外为人之学,而非切己向内之学。敬义工夫要求在念头思虑上用功,通过持养、省察双向并进之方,达到内直外方之效用。敬义是检点身心的实践工夫,格致是探究事理工夫,二者所主不同,应严格区分而不可混为一体。在与李燔的信中,他亦将检点身心与讲学穷理对立起来,痛斥流于讲学是儒道失传的罪魁祸首,强烈表达了应以身心点检为主的思想。《与李敬子司直书》言:
近读《中庸》,因推考古先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博文易而约礼难。后来学者专务其所易而常惮其所难,此道之所以无传……若
但务学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学问也。……独南康德契兄与诸贤维持,讲学最盛……但不知于身心上点检处如何耳。[22]
古代圣贤之学皆是就身心用工,如《书》之人心道心、《易》之直内方外,皆是论身心工夫而非讲学。夫子担心学者认识倾向一偏,故以博文与约礼对举,希望兼顾讲学之文与实践之礼。就先后论,博文在约礼之前;就难易论,约礼更甚于博文,而学者流于外在讲学而放弃了约礼工夫,直接导致道的失传。当以戒惧慎独工夫为补救之方,以之为毕生事业而时刻遵循,讲学穷理不过起讲明戒慎的辅助作用。如仅知讲学则丧失了学问根本,学问根本在于身心实践。南康虽然为目下师门讲学最盛之地,更应用功于身心检点。
勉斋反复指出检点身心的意义,以极为强烈的对比性措辞强调是否有检点工夫是人生分界所在。“不到此间议论,虽杀人放火,自不相干;既到此间议论,须是检点自己,从头到尾,得彻方是。”[23]晚年屡屡道及检点身心是人生唯一重要之事,百事皆当放下,唯独检点身心工夫不可丝毫放松。“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检点身心为急也。”[24]只有检点身心才能使人性光明、纯粹、洁净如初,而恢复本初,不负此生。“今亦他无所用心,只得检点身心,令明净纯洁,交还天地父母耳。”[25]
勉斋非常重视孟子的“求放心”说,认为此是极重要的身心工夫,提出“存心之学”与辞章记问之学的区别。人心受到物欲拖累,就会放荡奔跑,从而丧失天理之约束,故圣贤以战战兢兢的静存动察工夫,来确保本心的存在。孟子求放心说是对学者提出的真切警诫,事关儒家之道的传承,秦汉以来学者沉溺于辞章、记问之学而丧失了古人存心、求心之学,直到周程先生,方才接续道统。学者于动静寝食中,皆当时刻牢记“求放心”而不可须臾偏离之,此为读书穷理之根本。“且是以‘求放心’为本,一动一静、一寝一食,不可离此三字,便有以为之根本,然后可以读书玩理也。”[26]多次告诫学者读朱先生书,应加倍于求放心工夫,反复批评过于思索文义的行为。强调自家心灵是书本文义的主宰,不能以书本之说漫过身心,提出“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说,此与象山“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说精神颇有相通。并多方设法,诱导学者反归于求放心。
先生曰:“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可也。”又尝言,“学者役精神于文义而不反求诸心,终未免有口耳之学。”故于讲论之际,必宛转而归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27]
勉斋亦强调存念头的重要。指出作为工夫之首的戒惧,具有自然、简易、内在、当下的特点,一念即是,不待他求,不待外索。直接将之简化为当下一念,这与心学的当下说相通。《复黄会卿》言,“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28]如能存心,则念头存而不失的当下,万理皆在。“存心则一念存,万理具”。帝王之学亦不过是通过检束、防制其心,使念头皆合乎中道。穷理玩索工夫未能专注精一,原因在于“反身一念”未能做到。而贤愚之分的关键亦在于为学念头是在身心之内还是在其之外。
勉斋尽管凸显了心的本体义,推崇反身向内的“求心”工夫,但并未走向象山“心学”,而是坚持并发展了朱子学的主敬立场。为学首要是检点身心而非读书,检点身心之首则是持敬。“为学须先理会心,理会心先须持敬。”[29]主敬不仅是求放心之要旨,更是必须牢记于心、须臾不可离的“护身符”,是学者为学的必备之方,是儒家抗拒一切鬼魔上身的救命符。“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便是护身符。”[30]
勉斋身心内转之学,得到后人的继承认可。吴昌裔指出,勉斋以居敬集义为主的身心点检向内工夫,是对文公之学的进一步推阐。“先生体贴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是则文公有功于程氏,而先生有助于师门。”[31]勉斋“内转”之学在弟子双峰那里得到弘扬。除批评朱子“求放心”章对“心”的理解析为义理与知觉外,在牛山之木章双峰又提出同样的批评。双峰之学体现出追求合一、简易之学的特点,多处批评朱子之解过于分析,如批评朱子将“诚”与“道”析为“本、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等说过于支离;以知行交互解三达德又“头绪未免太多”等。
朱陆异同是朱子后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北溪表现出极力捍卫师门、抨击象山的态度,勉斋对陆学态度相对温和,认为其最大问题是“不读书”,但勉斋自身对读书的态度又颇矛盾,认为只是第二义,第一义是持敬收心,批评“后生辈皆以为读书者,充塞时文之具矣”[32]。双峰虽亦不满于象山不读书说,却提出“尊德性以为之本”说。如何看待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判定朱陆学者立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双峰后学的吴澄则更因力倡“尊德性为本”而被视为陆学,成为元代朱陆合流的代表。其中虽不无误解,但自朱子格物穷理到勉斋“点检身心”再至双峰、草庐“尊德性为本”,确乎显示出“后朱子学”演变的某种真实轨迹和趋向。
勉斋《论语》诠释,体现出对朱子学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重趋向,奠定了“后朱子学”经典诠释的基本样式,弘扬了朱子学的理性辨正精神,指引了朱子学转向内在身心的工夫路线,昭示了日后朱陆异同话题的彰显,对深入研究朱子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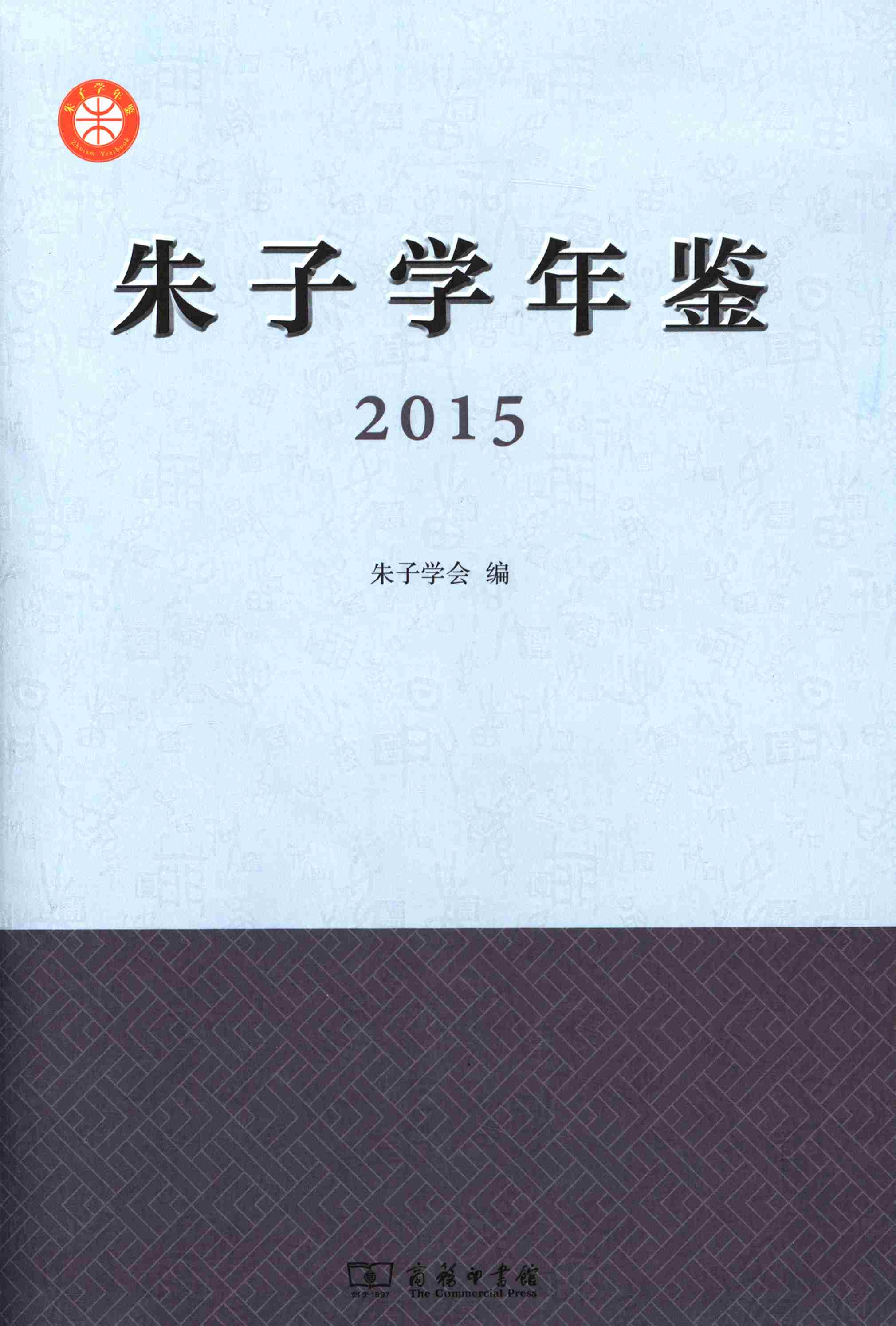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
相关人物
许家星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