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14 |
| 颗粒名称: |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9 |
| 页码: | 63-8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包括“心之全体大用”、“心之全体”的具体发用、朱子“全体大用”观的发展演变、几点思考情况。 |
| 关键词: | 朱子学 发展 演变 |
内容
朱子的格物致知既是知识论又是工夫论,是为学的起点,也是为道的起点,是明明德的工夫,“全体大用”思想则是其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然而,何谓“吾心之全体大用”?学术界对此语焉不详。回到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发现,“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就是“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就是仁,就是性体情用,就是心之动静,就是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就是圣人气象等。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影响深远,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以及东亚儒学对此都有不同的诠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心之全体大用”
朱子之学问,如浩瀚的大海,漫无涯际,令人望而生畏。朱子之博大实不可一言以尽之。如果勉强做一概括,我想答案应该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1]。朱子十分明确地表示,“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修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2]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第一义,儒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圣人创作《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所有人都能超凡入圣,一起进入圣人的境域,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格物”二字。四库馆臣也认为,“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3]
格物致知是为学的起点,是为道的起点,也是成圣的起点。何谓“格物”?何谓“致知”?朱子认为,《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于是仿照古人的意思写了一段“格物致知补传”,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的集中阐释,也是其晚年定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4]朱子认为,格就是到,物就是事。穷尽事物的道理,就要认识到极致即无所不到。致就是扩充、推广到极致,知就是识。扩充我的知识,就要做到知无不尽。这就是说,探求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奥秘,不可只停留在表面,要达到它的极处,即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只有持久努力,一旦豁然贯通,则事物的表里精粗、内心的全体大用都能彻底认知,获得一种彻悟性的知识,达到对最高天理的心领神会。这就叫作“物格”,叫作“知至”。“格物”之“物”,并非客观事物,“物犹事也”,尤指人伦物理,其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儒家价值的认同,格物致知乃在于确证内心固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寻找生命存在的社会意义与精神境界,以达到“全体大用”“心与理一”的最高觉悟和最高境界——道的境界、圣人境界。
概言之,朱子的格物致知的最后结果就是悟道,就是“豁然贯通”的悟的境界,具体所指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然而,这样一个彻悟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学术界多语焉不详。
格物致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工夫[5],悟道之后的境界分别对应两种境界,格物的结果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致知的结果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他们的最有利的证据似乎就是朱子回答剡伯问格物、致知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6]实质上,他们只看到第一句,而忽视了第二句。其实朱子格物致知的境界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是“合内外之道”的境界,既有外在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又有内在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二者的统一体。甚至,在朱子看来,“格物所以明此心。”[7]格物只要达到“里”的层面和“精”的层面,就开始达到“心”的全体大用的层面,就达到了“物格而后知至”的效果,“心”的全体大用才是格物的最终归宿。
那么,究竟什么是“表里精粗”呢?朱子认为,表里精粗首先指对“理”的认识的高低深浅。“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只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作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工夫,这唤作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8]“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晓其精,皆不可谓之格。”[9]朱子坚决反对只做表面工夫,不追求终极天理的学人。更反对那些仅仅追求内在真理,又嫌眼前道理粗浅,对事事物物都不理会的学人。理之“表里精粗”是一个整体,表与里、精与粗是天理的一体两面。如果认识达到“知得里,知得精”,二者就达到物格、知至的境地。
其次,表里指“人物之所共由”和“吾心之所独得”。“表者,人物之所共由;里者,吾心之所独得。表者,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
里者,乃是至隐至微,至亲至切,切要处。”[10]如果说,“表”是人物所共行之大道,是外在的,浅表的;那么,“里”就是我内心对大道的独特体认,它是非常隐秘、非常精微的,也是非常亲切可行的,是切中要害的。
再次,表里分别指“博我以文”和“约我以礼”。朱子回答弟子问表里时说:“所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是之谓表。至于‘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是之谓里。”[11]所谓“博我以文”,就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通透无遗,这是从外面的广博而言;所谓“约我以礼”,就是要像自家身心去探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未尽之处,这是从内在的精深处立言。朱子弟子子升感慨地说,自古学问亦不过这两件事情。朱子肯定了子升的观点,更加强调一定要看得通透、彻底,才能到达“知至”的境地。
最后,精粗指认知与境界之高下。朱子在回答弟子问精粗时说:“如管仲之仁,亦谓之仁,此是粗处。至精处,则颜子三月之后或违之。又如‘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充无欲穿窬之心,则义不可胜用’。害人与穿窬固为不仁不义,此是粗底。然其实一念不当,则为不仁不义处。”[12]管仲之“仁”不过是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天下百姓得以保全,故孔子称颂他的仁德,这是指“事”而言,只不过是“仁”的外在表现。[13]而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这是指“心”而言,这才是“仁”的精妙、精微的境界。
在朱子看来,认识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就达到了“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究竟什么是体?什么是全体?究竟什么是用?什么是大用?“安卿问‘全体大用’。曰:‘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此身全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问:‘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如何是体?如何是用?’曰:‘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淳录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体。’”[14]体与用不即不离,体就是用,用就是体。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朱子所称许的“全体大用”呢?
首先,在一般的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5]。”“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6]“明德”即“心之本体”,人心具有万事万物的道理而能自然而然地接应万事万物。但人心受到气质之性的局限,被物欲所遮蔽,有时候不能发出本来固有的光明的德性,“明明德”就是要回到原初那一片光明的德性中去,回归本心原有的澄明。“人之明德,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汩于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云: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则又似必着意体察然后有见。”[17“明德”之“全体大用”具体体现在伦常日用之中,政事的具体运用只是“明德”的向外推衍而已。如果没有觉察到内心的光明的道德,人们就容易沉湎于物欲而不自知,无法恢复本心的自觉与自知。
其次,全体大用一开始指仁体义用。天命之性流行发用于伦常日用和万事万物之中,其全体就是“仁”,万事万物对天命之性的分享和发用,各安其性,各尽其分,这就是义。“熹尝谓天命之性流行,发用见于日用之间,无一息之不然,无一物之不体,其大端全体即所谓仁,而于其间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毫厘之间,不可差谬,即所谓义。立人之道不过二者,而二者则初未尝相离也,是以学者求仁精义,亦未尝不相为用。”[18]仁义是人道的核心价值,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决然分割为二。朱子反对否定精义的空言,认为这是告子“义外”说的错误的根源。如果不知“义”而空谈“仁”,则尽不到仁的全体大用的功用。
再次,在心的运动变化的层面,“全体大用”又指心之动静而言。“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体大用……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岁工夫,屏除旧习,案上只看六经语孟及程氏文字,着开扩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会,方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真实语。”[19]又说:“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此其所以能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也。圆神,方知变化二者阙一则用不妙,用不妙则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20]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动静不失其时,能开物成务,世界一片光明祥和,这就是本心的全体大用。
第四,“全体大用”又指“仁”。朱子认为,“德是逐件上理会底,仁是全体大用,当依靠处。”又说:“据德,是因事发见底;如因事父有孝,由事君有忠。依仁,是本体不可须臾离底。据德,如着衣吃饭;依仁,如鼻之呼吸气。僩”[21]针对蜚卿的提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朱子回答说:“‘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道夫”[22]仁是全体大用,它的发用就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
第五,在推行方式上,全体大用即是推己及人,就是孔子之忠恕之道,即“仁”的具体推衍。“故圣人举此心之全体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达者达人,以己及物,无些私意。如尧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以至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道理都拥出来。人杰”[23]心的向外推衍、发用,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推己及人。尧通过明明德的工夫而达到和睦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天人合一,就是推己及人,就是把儒家忠恕之道发挥到极致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明代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指出:“求终身之行于一言,可谓善学矣!其恕乎!言举斯心推诸彼而已矣!心体与天下相关,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学者苟随所在而扩充之,则全体大用无不由此出矣。非终身可行之道哉?”[24]
第六,在心性结构上,全体大用指性体情用。在心性结构上,朱子主张心、性、情三分,心主性情,心统性情。贺孙因举《大学或问》云:“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元有一贯意思。贺孙”[25]心是心的主宰,心之全体就是仁义礼智之性,心的发用,就是人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性即理,人性之中本来就具有众理,本来就能明万善,只是由于气质和物欲的杂质掺杂其中故昏暗不明。因而,只有剔尽心性的杂质,才能回归心性的光明,回归心性原初的光明的本体。“窃谓人性本具众理,本明万善,由气质物欲之杂,所以昏蔽。上智之资无此杂,故一明尽明,无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杂,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则去得一分之杂,直待所见尽明。所杂尽去,本性方复。学者体此,以致复性之功。”[26]
第七,“全体大用”指“圣人气象”。格物致知即到达圣贤之域。“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纵有敏钝迟速之不同,头势也都自向那边去了。”“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夔孙”[27]格物致知所达到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就是圣贤觉悟之后的境界,每个人一旦优入圣域,圣贤气象油然而生。“夫子之道如天,惟颜子得之夫子许多。大意思尽在颜子身上发见,如天地生物即在物上尽见,天地纯粹之气谓之发者,乃亦足以发之,发不必待颜子言之而后发也。颜子所以发圣人之蕴,恐不可以一事言。盖圣人全体大用,无不一一于颜子身上发见也。”[28]朱子称许的颜子气象就是“圣人气象”,体现出圣人的“全体大用”。这是一种自然和乐、从容、纯粹、澄明的气象,如天地生养万物,自然显现,生机盎然,在万事万物上自然体现。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朱子认为,颜子作为亚圣,其精纯度可得九分,但与孔子的十分和圆熟相比,在境界上还略逊一筹。
二、“心之全体”的具体发用
表面上,朱子格物致知只是追求“心之全体大用”的境界,其实,格物致知所追求的“全体大用”也包含“理”之“全体大用”。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基本遵循的是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即从“德”到“治”的演变。后世许多思想家皆以“全体大用”为朱子理学的精神。[29]朱子充分肯定了弟子描述格物致知贯通之后的“心即理,理即心”的观点:“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先生所谓‘众理之精粗无不到’者,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吾心之光明照察无不周’者,全体大用无不明,随所诣而无不尽之谓……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30]这里的“心即理,理即心”与陆王心学不同,它指心与理不即不离,是格物致知的觉解境界,其实质就是“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意思。朱子强调,理必然有理之功用。“或问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31]朱子甚至声称,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个道理,外王之道与内圣之道也只是一个道理。所谓格物致知,也就是要知晓这个道理而已,这是《大学》一书的基本宗旨。“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颜回同道,岂必在位乃为为政哉!”[32]内圣外王之道,殊途同归,圣王与圣贤同道。大禹、后稷、颜回同道,并不是只有在位才能为政。
《大学》之道,内外一以贯之。“明德”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明德的使命就在于唤醒内在生命的主体自觉,唤醒自己内在光明的德性,排除物欲的遮蔽,回到原初光明澄澈的本心。这个原本光明澄澈的内心包含着万理,自然能应接万物,因而,明明德既是明此心,也是明此理。内心明德的向外推衍,也就是从修身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明此明德,觉此明德,存此明德,不为物欲所遮蔽,只不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更大、任务更重而已。“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所以《大学》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学,则能知觉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学》一书,若理会得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33明明德需要从切近的身心由近及远推至家国天下,明明德的发用就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功效。“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见处理会,也且慢慢自见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识得!……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尧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尧一国之明德;‘黎民于变时雍’,是尧天下之明德。”[34]在朱子看来,明明德不仅要明此心,明此理,还包含着知此理、行此理的意义。“盖所谓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与我一把火,将此火照物,则无不烛。自家若灭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时,又是明其明德。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阙一。若阙一,则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35]光明的本心、透彻的道理就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既照亮了自己的内心,也照亮了他人和整个世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明明德”的工夫,包含着尽知和尽行两个方面。格物、致知就是要知得分明,知到极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要行得分明,行到极处,二者的结合才是朱子的“全体大用”。
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并穷尽事物的道理,它需要在具体事物上落实。格物就是就着具体事物而做穷理的工夫,因此朱子特别强调《大学》以格物的入手工夫就是在于要在事上理会,即事明理,真知力行,否则所认识的道理只是一个悬空的道理。朱子认为:“人多把这道理做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36]朱子格物致知工夫的真正落实,是“知之深”和“行之至”,即真知的获得和实践的圆满完成。致知所获得的“知”是“真知”,既是具有真切的感性经验之知,又是能真切实行的真知。二程指出,“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木。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37]真知就能力行,知而不行,只是认知太浅薄,没有达到致知的目的。在朱子看来,格物致知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夫,它还诉诸行动,致知之“知”是“真知”,即能实行的真正的知识,那些不能真正落实为行动的知识谈不上是“真知”。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只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见识只识到那地位。譬诸穿窬,稍是个人,便不肯做,盖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伤事亦然。”[38]“‘反身而诚’,只是个真知。真实知得,则滔滔行将去,见得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39]只有圣贤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朱子认为,“反身而诚”便是真知。真的知得这个道理,气势磅礴地展开行动,直到见得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地,那种快乐才是无边无际的。朱子以格物致知建立理学,通过格物致知来贯通内在之理与外在之理,内心具备众多的理能自然应接万事万物,使得内外一体,心与理一,全体大用,知行一致。
“全体大用”的精神还必须在实践上予以落实,这也是“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子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有了“全体大用”的精神指引,朱子学在应接万事万物之中有所依仗。这一切不仅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充分体现在朱子书院教化、身心修炼、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理论与实践之中,它们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照亮了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与生活世界。
书院教育的推广。朱子是南宋书院教育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在南宋167所书院中,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有67所,占据40%以上,远远在同时代各位道学大师在之上,其对于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集中体现了朱子书院教化的理念。朱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40]《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作为为学的目标,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它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精神正是传统书院的首要精神。朱子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也就是实施道德教化,即用《尚书》标举的人伦教化于民众。它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道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朱子书院教化尤其重视“知行合一”,注重道德的践履。他接着说:“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41]笃行、修身、处事、接物,无不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笃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项认知的归宿,即把外在的求知转化为内在的生命,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在生命实践中展开落实。这样一来,书院之“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践履人伦则成为“为学”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即做到“穷理”和“笃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白鹿洞书院揭示》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学、问、思、辨,而把浓墨重彩涂抹在“修身”“处事”“接物”等“笃行”事务上,把知识的获得与身心修炼弥合得天衣无缝,这是典型的道学家的教化理念,足见朱子书院教化的经世关怀。[42]《白鹿洞书院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高度凝聚,影响久远,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科玉律。
朱子家礼的实践。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也是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朱子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和福建的民间婚礼基本遵从《朱子家礼》,郑志明先生还在台湾地区推广朱子丧礼,韩国和中国大陆对朱子祭礼都十分重视,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纪念日),韩国和中国大陆都会举行隆重的朱子祭礼仪式。与此关联的是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的勃兴壮大,家谱文化、祠堂文化、宗亲论坛等日益兴盛,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些文化实践活动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它也有力地证明了朱子家礼茂盛的生命力。
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社仓制度,系南宋朱子首创的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孝宗乾道四年(1168),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情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43]淳熙八年(1181),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44]。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它也充分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视民如子、天下一家的淑世情怀。正是通过身心—家—国—天下的一体建构,朱子理学的精神关切也从自我扩充到家族、国家和整个世界。
三、朱子“全体大用”观的发展演变
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对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乃至东亚世界影响深远[4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朱子后学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承传与创新。对于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其晚年得意门生陈淳的理解十分到位并适当发挥。“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圣贤存养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发也,全体卓然,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这里。及其动而应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尔而未尝有丝毫铢两之差,而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亦常自若而未尝与之俱往也。”[46]陈淳指出,心有体有用,“具众理”是体,“应万事”是用,心体寂然不动,这是指性之静而言,感而遂通是其发用,这是指情之动而言。圣贤存养工夫做得好,就能保持内心的贞定,其应接万事自然而然而没有丝毫的差错,这也是程颢、朱子极为推崇的“定性”的工夫和境界。朱子认为,定性就是明明德的工夫:“人心惟定则明。所谓定者,非是定于这里,全不修习,待他自明。惟是定后,却好去学。看来看去,久后自然彻。”[47]只有内心贞定,人心才能一片光明。朱子强调,定性之“定”,并非定在这里,完全不用修养工夫,而心之本体自然光明。[48]定性之后,一定要去学习、修炼,天长日久,自然就能看得透彻。应该肯定,陈淳的理解十分透彻十分系统,对朱子全体大用的四个层次区分得十分明晰。只是陈淳主要在解释“心”的观念,没有办法把“明德”“仁”及其发用、“圣贤气象”等内涵容纳进来。
朱子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的“全体大用”思想基本继承了朱子哲学的精神并有所创发,提出“明体达用”。真德秀认为,全体大用具体表现为“众理”与“万事”的体用关系,故全体大用又可以表达为:“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理即事,事即理”又指理与事(物)之间的体用关系,“体”指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用”指发为实践实行之事。真德秀认为:“大抵理之于事,元非二物。……惟圣贤之学,则以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二者相须,本无二致,此所以为无蔽也。”[49]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在事中,事在理中。真德秀进一步指出,学者求学无非就是穷理以致用,理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用途,功用必定有终极的原理,理就是用,用就是理。“独尝窃谓士之于学,穷理致用而已。理必达于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50]在这里,真德秀批判了佛老(异端)脱离事物空言道理,最后陷入空疏无用;而仅言事实而忽视大道,最终游于无根的粗浅之谈。只有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即用,用即理,二者融会贯通才能称之为学之成。但是怎样才能称为“学之成”呢?真德秀的解答十分精到——“成己成物”,这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为”主要就事功而言。古圣先贤的“为仁”“为邦”分别代表成己成物的极致,它期许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的实现,也即由内圣推至外王,完成王者的事功,建立王者的丰功伟绩,儒学的体用本末都集中体现在这里。
真西山之学,即“明体达用”之学。真德秀极力反对那种把儒家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割裂为二的做法,他说:“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近世顾析而二焉。尚详世变者,指经术为迂;喜谈性命者,诋史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然则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为道之大全乎?故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天理不达诸事,其弊为无用。事不根诸理,其失为亡本。吾未见其可相离也。”[51]真德秀认为,儒家学问有经有史,性命道德之学是经,古今世变之学是史;同时前者又是个“理”,后者则是个“用”。换言之,“成己”是体,“成物”是用;内圣是体,外王是用。善学者应该本经参史、经史互证,这样才能“明理达用”,可见,真德秀努力在内圣和外王之间找到一个调和之处。蒙培元也认为,提倡“经史并用”、要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是真德秀学术的特色,这一点是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52后世多称道他的学说“有体有用”“明体达用”。清代张伯行说:“先生之学卓然有体有用,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也。”[53]清代雷也称:“先生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54]
真德秀还认为《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他运用朱子“全体大用”思想来推衍和阐释《大学》,著成《大学衍义》一书。朱子十分重视《大学》,他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55]又曰:“今且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56]可惜朱子未能完成这一设想,它的完成就是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真德秀指出:“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57]《大学衍义》一书的目的就是让人君明白尧舜禹的体用之学,由内在的修身养性而达之天下,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元代学者对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颇为平淡。元代大儒许谦认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全体即前具众理,大用即前应万事。”“表里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亲其道当孝,此是表;如《孝经》一书之中有许多节目,又诸书言孝节目不一,此是里。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谓其间事为礼节也。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谓事为礼节中之至理也。”[58]许谦对全体大用的理解没有太多的创新,但他对“表里精粗”有所推进,认为,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粗与精的关系于是巧妙地转化为事与理的关系。新安陈栎则基本沿袭了朱子对“全体大用”的理解,他指出,“久字与一旦字相应用力,积累多时,然后一朝脱然通透,吾心之全体即释明德章句所谓具众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谓应万事者也。”[59]元代朱子后学熊禾在他的《考亭书院记》一文中充分肯定朱子之学就是全体大用之学,表现出德与治、本与末的内在关联。“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60]朱子之学还继承了伏羲以来的道统,使得古圣先贤的全体大用之学重新大放光明。
明代邱浚对朱子的全体大用进行了系统的发挥和诠释,尤其重视其中的治道和致用。他认为,全体大用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朱子之学即圣门“全体大用”之学。“朱子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择焉而精,其在章句。语焉而详,其在或问乎。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其朱子自道欤。”“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则为伯道,用非其用,无体故也。学而外此则为异端,体非其体,无用故也。”[61]邱浚指出,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为学者不能离开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来追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离开《大学章句》《或问》来成就帝王之伟业。离开了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治道也就成了有用无体的霸道,治学则是有体无用的异端之学。
其次,《大学》为儒者全体大用之学。“《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62]“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63]在邱浚看来,《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是六经的浓缩精华版,不愧为儒家的全体大用之学的经典文本。邱浚尤其关注《大学》治国、平天下之方略,其《大学衍义补》集中衍义了《大学》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
第三,《易》者其体,《书》者其用。“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64]《易》乃群经之首,义理之宗,学者学习六经成为儒者,讲明义理并以此修身,这就是“全体”之学。其“大用”则表现为治人与为政,它也是学的完成。《书》经是古圣先贤为政的文献,最能体现政治的精神。
第四,“横渠四句”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表达。“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65圣人全体大用之学关乎道统的承传。“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66]从伏羲、尧、舜、禹、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这些圣人都在为有形而无心之天地立心,为有命而不能自遂之生民立命,使得凡夫俗子皆有机会优入圣域。而曾子的《大学》之教,则是为了承接孔子之精神和往圣之精神,接续道统,为万世开太平,承传圣人全体大用之学。横渠的“四句教”则是对《大学》全体大用思想的精练表达,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体现。
最后,全体大用又指“圣德之全体大用”。“臣按:朱熹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67]“圣德之全体大用”指向的是内心至圣之德,它来源于上天“至诚之道”,唯有聪明圣知的圣人才能上达天德,才能完成“全体大用”的功效,实现“全体大用的境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尧舜这样的圣王,邱浚勉励帝王要有所作为,要向三代学习,向尧舜学习,上达天德,成为一代圣君。
四、几点思考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全体”就是心中包含所有的道理,所谓“大用”就是人心自然能应接万事万物。“全体大用”精神落实在实际的社会政治层面,就是朱子书院教化的实践、朱子社仓的建立以及《朱子家礼》的推广,而作为学术层面展开则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礼制研究,足见朱子思想中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致知与力行的统一。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承传与创新,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走向东亚世界,成为东亚思想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仔细梳理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
(一)隐藏在“全体大用”话语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
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68](Barbara Johnstone,第102页)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全体大用”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透过朱子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朱子对内圣精神的推崇,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微言大义”的传统。具体而言,“全体大用”除了朱子《大学章句》所标榜的“明德”和“心具众理而应万事”,还有仁体义用、性体情用、心之动静、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圣人气象等不同的含义,这些内涵在“全体大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结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它们隐藏在结论的背后,被历史所遮蔽。从“仁体义用”到“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朱子哲学所经历的从片面到不断完善的艰辛历程。“全体大用”思想在朱子哲学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揭示,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朱子哲学的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只是朱子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只是其格物致知理论的一个环节。朱子的“格物”只是“明此心”,“全体大用”只是“心”之“全体大用”。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必须回到朱子哲学的心性语境中来定位。“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属于修身的功夫,它的向外发用可以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外在的功用只是心的作用的外推和放大,尽管朱子有诸多的社会关切,但在本质上它仍然属于心性儒学。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社会功用也不宜过分放大,朱子的活动更多还是在书院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其社会事功总体来说建树不大,其在漳州任内正经界和晚年出任帝王师等活动则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也与他的内在于心性的“全体大用”思想紧密相关。
(二)“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
话语具有建构知识和社会的能力。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和沃戴克(R.Wodak)把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概括为: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权力关系是“话语的”(discursive),即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变化的场所;话语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69]后世对朱子的理解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全体大用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它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在陈淳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仍然是一种真理权威,一种知识权力,只是在帮助他们完成心性知识的建构。师生知识共同体,朱子的思想与弟子的思想内部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真德秀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开始获得社会权力,走向权力的中心。元代朱子后学又走向了心性儒学的回归,明代邱浚则在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引导全体大用走向帝王之学。可见,后世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经历了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的互动。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后世对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和演化也基本演绎着德与治、内圣与外王的思想进路。
(三)从“全体大用”的视角重新审视朱子的心与理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后世对其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朱子思想体系的理解。“全体大用”是格物的最后境界和归宿,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最高天理的认识。天理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心”与“理”是“一”还是“二”,二者的分野构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界线。牟宗三先生认为,“心具众理”是认知地具,及“既格”而现实地具之,此理固内在于心矣,然此“内在”是认知地摄之之内在,仍非孟子“仁义内在”之本体地固具之之内在。此种“内在”并不足以抵御“理外”之疑难。此仍是心理为二也。二即是外。[70](牟宗三,第368页)朱子思想的主旨为理学,理是根源性存在,是最高的实体。但并不表示此理只是心外之理,心与理截然为二。朱子虽然承认一物有一物之理,但他的格物就是“明此心”,“明此理”,是“明明德”的工夫。格物致知所到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心”不仅“具众理”,而且“包万理”,还能知“万理”。尽管朱子从本体论上坚决反对“心即理”,但“理”在心中,心具众理。心知众理,心管众理。所谓“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朱子语类》卷十八)一句话,在朱子的思想世界里,理为体,心为用,心包万理,心管万理,全体大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朱子指出,“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朱子语类》卷五)这种“心与理一”的境界,指心与理交相辉映,融为一体,随事而发,物来顺应,自然而然。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心学与理学对“心与理”的区分十分清晰,但在认识论和境界论意义上,“心与理一”是心学与理学家共同信守的基本理念和终极关怀。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哲学系)
一、“心之全体大用”
朱子之学问,如浩瀚的大海,漫无涯际,令人望而生畏。朱子之博大实不可一言以尽之。如果勉强做一概括,我想答案应该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1]。朱子十分明确地表示,“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修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2]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第一义,儒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圣人创作《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所有人都能超凡入圣,一起进入圣人的境域,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格物”二字。四库馆臣也认为,“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3]
格物致知是为学的起点,是为道的起点,也是成圣的起点。何谓“格物”?何谓“致知”?朱子认为,《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于是仿照古人的意思写了一段“格物致知补传”,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的集中阐释,也是其晚年定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4]朱子认为,格就是到,物就是事。穷尽事物的道理,就要认识到极致即无所不到。致就是扩充、推广到极致,知就是识。扩充我的知识,就要做到知无不尽。这就是说,探求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奥秘,不可只停留在表面,要达到它的极处,即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只有持久努力,一旦豁然贯通,则事物的表里精粗、内心的全体大用都能彻底认知,获得一种彻悟性的知识,达到对最高天理的心领神会。这就叫作“物格”,叫作“知至”。“格物”之“物”,并非客观事物,“物犹事也”,尤指人伦物理,其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儒家价值的认同,格物致知乃在于确证内心固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寻找生命存在的社会意义与精神境界,以达到“全体大用”“心与理一”的最高觉悟和最高境界——道的境界、圣人境界。
概言之,朱子的格物致知的最后结果就是悟道,就是“豁然贯通”的悟的境界,具体所指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然而,这样一个彻悟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学术界多语焉不详。
格物致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工夫[5],悟道之后的境界分别对应两种境界,格物的结果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致知的结果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他们的最有利的证据似乎就是朱子回答剡伯问格物、致知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6]实质上,他们只看到第一句,而忽视了第二句。其实朱子格物致知的境界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是“合内外之道”的境界,既有外在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又有内在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二者的统一体。甚至,在朱子看来,“格物所以明此心。”[7]格物只要达到“里”的层面和“精”的层面,就开始达到“心”的全体大用的层面,就达到了“物格而后知至”的效果,“心”的全体大用才是格物的最终归宿。
那么,究竟什么是“表里精粗”呢?朱子认为,表里精粗首先指对“理”的认识的高低深浅。“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只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作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工夫,这唤作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8]“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晓其精,皆不可谓之格。”[9]朱子坚决反对只做表面工夫,不追求终极天理的学人。更反对那些仅仅追求内在真理,又嫌眼前道理粗浅,对事事物物都不理会的学人。理之“表里精粗”是一个整体,表与里、精与粗是天理的一体两面。如果认识达到“知得里,知得精”,二者就达到物格、知至的境地。
其次,表里指“人物之所共由”和“吾心之所独得”。“表者,人物之所共由;里者,吾心之所独得。表者,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
里者,乃是至隐至微,至亲至切,切要处。”[10]如果说,“表”是人物所共行之大道,是外在的,浅表的;那么,“里”就是我内心对大道的独特体认,它是非常隐秘、非常精微的,也是非常亲切可行的,是切中要害的。
再次,表里分别指“博我以文”和“约我以礼”。朱子回答弟子问表里时说:“所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是之谓表。至于‘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是之谓里。”[11]所谓“博我以文”,就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通透无遗,这是从外面的广博而言;所谓“约我以礼”,就是要像自家身心去探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未尽之处,这是从内在的精深处立言。朱子弟子子升感慨地说,自古学问亦不过这两件事情。朱子肯定了子升的观点,更加强调一定要看得通透、彻底,才能到达“知至”的境地。
最后,精粗指认知与境界之高下。朱子在回答弟子问精粗时说:“如管仲之仁,亦谓之仁,此是粗处。至精处,则颜子三月之后或违之。又如‘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充无欲穿窬之心,则义不可胜用’。害人与穿窬固为不仁不义,此是粗底。然其实一念不当,则为不仁不义处。”[12]管仲之“仁”不过是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天下百姓得以保全,故孔子称颂他的仁德,这是指“事”而言,只不过是“仁”的外在表现。[13]而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这是指“心”而言,这才是“仁”的精妙、精微的境界。
在朱子看来,认识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就达到了“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究竟什么是体?什么是全体?究竟什么是用?什么是大用?“安卿问‘全体大用’。曰:‘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此身全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问:‘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如何是体?如何是用?’曰:‘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淳录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体。’”[14]体与用不即不离,体就是用,用就是体。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朱子所称许的“全体大用”呢?
首先,在一般的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5]。”“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6]“明德”即“心之本体”,人心具有万事万物的道理而能自然而然地接应万事万物。但人心受到气质之性的局限,被物欲所遮蔽,有时候不能发出本来固有的光明的德性,“明明德”就是要回到原初那一片光明的德性中去,回归本心原有的澄明。“人之明德,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汩于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云: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则又似必着意体察然后有见。”[17“明德”之“全体大用”具体体现在伦常日用之中,政事的具体运用只是“明德”的向外推衍而已。如果没有觉察到内心的光明的道德,人们就容易沉湎于物欲而不自知,无法恢复本心的自觉与自知。
其次,全体大用一开始指仁体义用。天命之性流行发用于伦常日用和万事万物之中,其全体就是“仁”,万事万物对天命之性的分享和发用,各安其性,各尽其分,这就是义。“熹尝谓天命之性流行,发用见于日用之间,无一息之不然,无一物之不体,其大端全体即所谓仁,而于其间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毫厘之间,不可差谬,即所谓义。立人之道不过二者,而二者则初未尝相离也,是以学者求仁精义,亦未尝不相为用。”[18]仁义是人道的核心价值,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决然分割为二。朱子反对否定精义的空言,认为这是告子“义外”说的错误的根源。如果不知“义”而空谈“仁”,则尽不到仁的全体大用的功用。
再次,在心的运动变化的层面,“全体大用”又指心之动静而言。“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体大用……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岁工夫,屏除旧习,案上只看六经语孟及程氏文字,着开扩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会,方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真实语。”[19]又说:“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此其所以能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也。圆神,方知变化二者阙一则用不妙,用不妙则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20]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动静不失其时,能开物成务,世界一片光明祥和,这就是本心的全体大用。
第四,“全体大用”又指“仁”。朱子认为,“德是逐件上理会底,仁是全体大用,当依靠处。”又说:“据德,是因事发见底;如因事父有孝,由事君有忠。依仁,是本体不可须臾离底。据德,如着衣吃饭;依仁,如鼻之呼吸气。僩”[21]针对蜚卿的提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朱子回答说:“‘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道夫”[22]仁是全体大用,它的发用就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
第五,在推行方式上,全体大用即是推己及人,就是孔子之忠恕之道,即“仁”的具体推衍。“故圣人举此心之全体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达者达人,以己及物,无些私意。如尧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以至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道理都拥出来。人杰”[23]心的向外推衍、发用,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推己及人。尧通过明明德的工夫而达到和睦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天人合一,就是推己及人,就是把儒家忠恕之道发挥到极致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明代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指出:“求终身之行于一言,可谓善学矣!其恕乎!言举斯心推诸彼而已矣!心体与天下相关,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学者苟随所在而扩充之,则全体大用无不由此出矣。非终身可行之道哉?”[24]
第六,在心性结构上,全体大用指性体情用。在心性结构上,朱子主张心、性、情三分,心主性情,心统性情。贺孙因举《大学或问》云:“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元有一贯意思。贺孙”[25]心是心的主宰,心之全体就是仁义礼智之性,心的发用,就是人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性即理,人性之中本来就具有众理,本来就能明万善,只是由于气质和物欲的杂质掺杂其中故昏暗不明。因而,只有剔尽心性的杂质,才能回归心性的光明,回归心性原初的光明的本体。“窃谓人性本具众理,本明万善,由气质物欲之杂,所以昏蔽。上智之资无此杂,故一明尽明,无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杂,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则去得一分之杂,直待所见尽明。所杂尽去,本性方复。学者体此,以致复性之功。”[26]
第七,“全体大用”指“圣人气象”。格物致知即到达圣贤之域。“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纵有敏钝迟速之不同,头势也都自向那边去了。”“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夔孙”[27]格物致知所达到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就是圣贤觉悟之后的境界,每个人一旦优入圣域,圣贤气象油然而生。“夫子之道如天,惟颜子得之夫子许多。大意思尽在颜子身上发见,如天地生物即在物上尽见,天地纯粹之气谓之发者,乃亦足以发之,发不必待颜子言之而后发也。颜子所以发圣人之蕴,恐不可以一事言。盖圣人全体大用,无不一一于颜子身上发见也。”[28]朱子称许的颜子气象就是“圣人气象”,体现出圣人的“全体大用”。这是一种自然和乐、从容、纯粹、澄明的气象,如天地生养万物,自然显现,生机盎然,在万事万物上自然体现。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朱子认为,颜子作为亚圣,其精纯度可得九分,但与孔子的十分和圆熟相比,在境界上还略逊一筹。
二、“心之全体”的具体发用
表面上,朱子格物致知只是追求“心之全体大用”的境界,其实,格物致知所追求的“全体大用”也包含“理”之“全体大用”。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基本遵循的是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即从“德”到“治”的演变。后世许多思想家皆以“全体大用”为朱子理学的精神。[29]朱子充分肯定了弟子描述格物致知贯通之后的“心即理,理即心”的观点:“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先生所谓‘众理之精粗无不到’者,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吾心之光明照察无不周’者,全体大用无不明,随所诣而无不尽之谓……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30]这里的“心即理,理即心”与陆王心学不同,它指心与理不即不离,是格物致知的觉解境界,其实质就是“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意思。朱子强调,理必然有理之功用。“或问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31]朱子甚至声称,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个道理,外王之道与内圣之道也只是一个道理。所谓格物致知,也就是要知晓这个道理而已,这是《大学》一书的基本宗旨。“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颜回同道,岂必在位乃为为政哉!”[32]内圣外王之道,殊途同归,圣王与圣贤同道。大禹、后稷、颜回同道,并不是只有在位才能为政。
《大学》之道,内外一以贯之。“明德”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明德的使命就在于唤醒内在生命的主体自觉,唤醒自己内在光明的德性,排除物欲的遮蔽,回到原初光明澄澈的本心。这个原本光明澄澈的内心包含着万理,自然能应接万物,因而,明明德既是明此心,也是明此理。内心明德的向外推衍,也就是从修身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明此明德,觉此明德,存此明德,不为物欲所遮蔽,只不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更大、任务更重而已。“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所以《大学》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学,则能知觉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学》一书,若理会得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33明明德需要从切近的身心由近及远推至家国天下,明明德的发用就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功效。“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见处理会,也且慢慢自见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识得!……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尧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尧一国之明德;‘黎民于变时雍’,是尧天下之明德。”[34]在朱子看来,明明德不仅要明此心,明此理,还包含着知此理、行此理的意义。“盖所谓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与我一把火,将此火照物,则无不烛。自家若灭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时,又是明其明德。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阙一。若阙一,则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35]光明的本心、透彻的道理就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既照亮了自己的内心,也照亮了他人和整个世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明明德”的工夫,包含着尽知和尽行两个方面。格物、致知就是要知得分明,知到极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要行得分明,行到极处,二者的结合才是朱子的“全体大用”。
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并穷尽事物的道理,它需要在具体事物上落实。格物就是就着具体事物而做穷理的工夫,因此朱子特别强调《大学》以格物的入手工夫就是在于要在事上理会,即事明理,真知力行,否则所认识的道理只是一个悬空的道理。朱子认为:“人多把这道理做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36]朱子格物致知工夫的真正落实,是“知之深”和“行之至”,即真知的获得和实践的圆满完成。致知所获得的“知”是“真知”,既是具有真切的感性经验之知,又是能真切实行的真知。二程指出,“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木。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37]真知就能力行,知而不行,只是认知太浅薄,没有达到致知的目的。在朱子看来,格物致知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夫,它还诉诸行动,致知之“知”是“真知”,即能实行的真正的知识,那些不能真正落实为行动的知识谈不上是“真知”。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只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见识只识到那地位。譬诸穿窬,稍是个人,便不肯做,盖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伤事亦然。”[38]“‘反身而诚’,只是个真知。真实知得,则滔滔行将去,见得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39]只有圣贤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朱子认为,“反身而诚”便是真知。真的知得这个道理,气势磅礴地展开行动,直到见得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地,那种快乐才是无边无际的。朱子以格物致知建立理学,通过格物致知来贯通内在之理与外在之理,内心具备众多的理能自然应接万事万物,使得内外一体,心与理一,全体大用,知行一致。
“全体大用”的精神还必须在实践上予以落实,这也是“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子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有了“全体大用”的精神指引,朱子学在应接万事万物之中有所依仗。这一切不仅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充分体现在朱子书院教化、身心修炼、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理论与实践之中,它们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照亮了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与生活世界。
书院教育的推广。朱子是南宋书院教育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在南宋167所书院中,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有67所,占据40%以上,远远在同时代各位道学大师在之上,其对于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集中体现了朱子书院教化的理念。朱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40]《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作为为学的目标,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它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精神正是传统书院的首要精神。朱子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也就是实施道德教化,即用《尚书》标举的人伦教化于民众。它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道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朱子书院教化尤其重视“知行合一”,注重道德的践履。他接着说:“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41]笃行、修身、处事、接物,无不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笃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项认知的归宿,即把外在的求知转化为内在的生命,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在生命实践中展开落实。这样一来,书院之“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践履人伦则成为“为学”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即做到“穷理”和“笃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白鹿洞书院揭示》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学、问、思、辨,而把浓墨重彩涂抹在“修身”“处事”“接物”等“笃行”事务上,把知识的获得与身心修炼弥合得天衣无缝,这是典型的道学家的教化理念,足见朱子书院教化的经世关怀。[42]《白鹿洞书院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高度凝聚,影响久远,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科玉律。
朱子家礼的实践。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也是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朱子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和福建的民间婚礼基本遵从《朱子家礼》,郑志明先生还在台湾地区推广朱子丧礼,韩国和中国大陆对朱子祭礼都十分重视,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纪念日),韩国和中国大陆都会举行隆重的朱子祭礼仪式。与此关联的是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的勃兴壮大,家谱文化、祠堂文化、宗亲论坛等日益兴盛,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些文化实践活动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它也有力地证明了朱子家礼茂盛的生命力。
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社仓制度,系南宋朱子首创的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孝宗乾道四年(1168),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情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43]淳熙八年(1181),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44]。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它也充分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视民如子、天下一家的淑世情怀。正是通过身心—家—国—天下的一体建构,朱子理学的精神关切也从自我扩充到家族、国家和整个世界。
三、朱子“全体大用”观的发展演变
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对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乃至东亚世界影响深远[4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朱子后学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承传与创新。对于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其晚年得意门生陈淳的理解十分到位并适当发挥。“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圣贤存养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发也,全体卓然,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这里。及其动而应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尔而未尝有丝毫铢两之差,而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亦常自若而未尝与之俱往也。”[46]陈淳指出,心有体有用,“具众理”是体,“应万事”是用,心体寂然不动,这是指性之静而言,感而遂通是其发用,这是指情之动而言。圣贤存养工夫做得好,就能保持内心的贞定,其应接万事自然而然而没有丝毫的差错,这也是程颢、朱子极为推崇的“定性”的工夫和境界。朱子认为,定性就是明明德的工夫:“人心惟定则明。所谓定者,非是定于这里,全不修习,待他自明。惟是定后,却好去学。看来看去,久后自然彻。”[47]只有内心贞定,人心才能一片光明。朱子强调,定性之“定”,并非定在这里,完全不用修养工夫,而心之本体自然光明。[48]定性之后,一定要去学习、修炼,天长日久,自然就能看得透彻。应该肯定,陈淳的理解十分透彻十分系统,对朱子全体大用的四个层次区分得十分明晰。只是陈淳主要在解释“心”的观念,没有办法把“明德”“仁”及其发用、“圣贤气象”等内涵容纳进来。
朱子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的“全体大用”思想基本继承了朱子哲学的精神并有所创发,提出“明体达用”。真德秀认为,全体大用具体表现为“众理”与“万事”的体用关系,故全体大用又可以表达为:“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理即事,事即理”又指理与事(物)之间的体用关系,“体”指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用”指发为实践实行之事。真德秀认为:“大抵理之于事,元非二物。……惟圣贤之学,则以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二者相须,本无二致,此所以为无蔽也。”[49]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在事中,事在理中。真德秀进一步指出,学者求学无非就是穷理以致用,理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用途,功用必定有终极的原理,理就是用,用就是理。“独尝窃谓士之于学,穷理致用而已。理必达于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50]在这里,真德秀批判了佛老(异端)脱离事物空言道理,最后陷入空疏无用;而仅言事实而忽视大道,最终游于无根的粗浅之谈。只有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即用,用即理,二者融会贯通才能称之为学之成。但是怎样才能称为“学之成”呢?真德秀的解答十分精到——“成己成物”,这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为”主要就事功而言。古圣先贤的“为仁”“为邦”分别代表成己成物的极致,它期许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的实现,也即由内圣推至外王,完成王者的事功,建立王者的丰功伟绩,儒学的体用本末都集中体现在这里。
真西山之学,即“明体达用”之学。真德秀极力反对那种把儒家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割裂为二的做法,他说:“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近世顾析而二焉。尚详世变者,指经术为迂;喜谈性命者,诋史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然则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为道之大全乎?故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天理不达诸事,其弊为无用。事不根诸理,其失为亡本。吾未见其可相离也。”[51]真德秀认为,儒家学问有经有史,性命道德之学是经,古今世变之学是史;同时前者又是个“理”,后者则是个“用”。换言之,“成己”是体,“成物”是用;内圣是体,外王是用。善学者应该本经参史、经史互证,这样才能“明理达用”,可见,真德秀努力在内圣和外王之间找到一个调和之处。蒙培元也认为,提倡“经史并用”、要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是真德秀学术的特色,这一点是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52后世多称道他的学说“有体有用”“明体达用”。清代张伯行说:“先生之学卓然有体有用,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也。”[53]清代雷也称:“先生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54]
真德秀还认为《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他运用朱子“全体大用”思想来推衍和阐释《大学》,著成《大学衍义》一书。朱子十分重视《大学》,他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55]又曰:“今且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56]可惜朱子未能完成这一设想,它的完成就是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真德秀指出:“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57]《大学衍义》一书的目的就是让人君明白尧舜禹的体用之学,由内在的修身养性而达之天下,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元代学者对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颇为平淡。元代大儒许谦认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全体即前具众理,大用即前应万事。”“表里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亲其道当孝,此是表;如《孝经》一书之中有许多节目,又诸书言孝节目不一,此是里。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谓其间事为礼节也。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谓事为礼节中之至理也。”[58]许谦对全体大用的理解没有太多的创新,但他对“表里精粗”有所推进,认为,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粗与精的关系于是巧妙地转化为事与理的关系。新安陈栎则基本沿袭了朱子对“全体大用”的理解,他指出,“久字与一旦字相应用力,积累多时,然后一朝脱然通透,吾心之全体即释明德章句所谓具众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谓应万事者也。”[59]元代朱子后学熊禾在他的《考亭书院记》一文中充分肯定朱子之学就是全体大用之学,表现出德与治、本与末的内在关联。“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60]朱子之学还继承了伏羲以来的道统,使得古圣先贤的全体大用之学重新大放光明。
明代邱浚对朱子的全体大用进行了系统的发挥和诠释,尤其重视其中的治道和致用。他认为,全体大用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朱子之学即圣门“全体大用”之学。“朱子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择焉而精,其在章句。语焉而详,其在或问乎。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其朱子自道欤。”“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则为伯道,用非其用,无体故也。学而外此则为异端,体非其体,无用故也。”[61]邱浚指出,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为学者不能离开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来追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离开《大学章句》《或问》来成就帝王之伟业。离开了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治道也就成了有用无体的霸道,治学则是有体无用的异端之学。
其次,《大学》为儒者全体大用之学。“《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62]“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63]在邱浚看来,《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是六经的浓缩精华版,不愧为儒家的全体大用之学的经典文本。邱浚尤其关注《大学》治国、平天下之方略,其《大学衍义补》集中衍义了《大学》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
第三,《易》者其体,《书》者其用。“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64]《易》乃群经之首,义理之宗,学者学习六经成为儒者,讲明义理并以此修身,这就是“全体”之学。其“大用”则表现为治人与为政,它也是学的完成。《书》经是古圣先贤为政的文献,最能体现政治的精神。
第四,“横渠四句”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表达。“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65圣人全体大用之学关乎道统的承传。“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66]从伏羲、尧、舜、禹、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这些圣人都在为有形而无心之天地立心,为有命而不能自遂之生民立命,使得凡夫俗子皆有机会优入圣域。而曾子的《大学》之教,则是为了承接孔子之精神和往圣之精神,接续道统,为万世开太平,承传圣人全体大用之学。横渠的“四句教”则是对《大学》全体大用思想的精练表达,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体现。
最后,全体大用又指“圣德之全体大用”。“臣按:朱熹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67]“圣德之全体大用”指向的是内心至圣之德,它来源于上天“至诚之道”,唯有聪明圣知的圣人才能上达天德,才能完成“全体大用”的功效,实现“全体大用的境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尧舜这样的圣王,邱浚勉励帝王要有所作为,要向三代学习,向尧舜学习,上达天德,成为一代圣君。
四、几点思考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全体”就是心中包含所有的道理,所谓“大用”就是人心自然能应接万事万物。“全体大用”精神落实在实际的社会政治层面,就是朱子书院教化的实践、朱子社仓的建立以及《朱子家礼》的推广,而作为学术层面展开则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礼制研究,足见朱子思想中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致知与力行的统一。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承传与创新,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走向东亚世界,成为东亚思想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仔细梳理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
(一)隐藏在“全体大用”话语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
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68](Barbara Johnstone,第102页)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全体大用”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透过朱子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朱子对内圣精神的推崇,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微言大义”的传统。具体而言,“全体大用”除了朱子《大学章句》所标榜的“明德”和“心具众理而应万事”,还有仁体义用、性体情用、心之动静、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圣人气象等不同的含义,这些内涵在“全体大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结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它们隐藏在结论的背后,被历史所遮蔽。从“仁体义用”到“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朱子哲学所经历的从片面到不断完善的艰辛历程。“全体大用”思想在朱子哲学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揭示,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朱子哲学的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只是朱子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只是其格物致知理论的一个环节。朱子的“格物”只是“明此心”,“全体大用”只是“心”之“全体大用”。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必须回到朱子哲学的心性语境中来定位。“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属于修身的功夫,它的向外发用可以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外在的功用只是心的作用的外推和放大,尽管朱子有诸多的社会关切,但在本质上它仍然属于心性儒学。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社会功用也不宜过分放大,朱子的活动更多还是在书院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其社会事功总体来说建树不大,其在漳州任内正经界和晚年出任帝王师等活动则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也与他的内在于心性的“全体大用”思想紧密相关。
(二)“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
话语具有建构知识和社会的能力。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和沃戴克(R.Wodak)把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概括为: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权力关系是“话语的”(discursive),即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变化的场所;话语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69]后世对朱子的理解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全体大用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它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在陈淳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仍然是一种真理权威,一种知识权力,只是在帮助他们完成心性知识的建构。师生知识共同体,朱子的思想与弟子的思想内部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真德秀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开始获得社会权力,走向权力的中心。元代朱子后学又走向了心性儒学的回归,明代邱浚则在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引导全体大用走向帝王之学。可见,后世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经历了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的互动。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后世对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和演化也基本演绎着德与治、内圣与外王的思想进路。
(三)从“全体大用”的视角重新审视朱子的心与理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后世对其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朱子思想体系的理解。“全体大用”是格物的最后境界和归宿,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最高天理的认识。天理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心”与“理”是“一”还是“二”,二者的分野构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界线。牟宗三先生认为,“心具众理”是认知地具,及“既格”而现实地具之,此理固内在于心矣,然此“内在”是认知地摄之之内在,仍非孟子“仁义内在”之本体地固具之之内在。此种“内在”并不足以抵御“理外”之疑难。此仍是心理为二也。二即是外。[70](牟宗三,第368页)朱子思想的主旨为理学,理是根源性存在,是最高的实体。但并不表示此理只是心外之理,心与理截然为二。朱子虽然承认一物有一物之理,但他的格物就是“明此心”,“明此理”,是“明明德”的工夫。格物致知所到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心”不仅“具众理”,而且“包万理”,还能知“万理”。尽管朱子从本体论上坚决反对“心即理”,但“理”在心中,心具众理。心知众理,心管众理。所谓“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朱子语类》卷十八)一句话,在朱子的思想世界里,理为体,心为用,心包万理,心管万理,全体大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朱子指出,“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朱子语类》卷五)这种“心与理一”的境界,指心与理交相辉映,融为一体,随事而发,物来顺应,自然而然。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心学与理学对“心与理”的区分十分清晰,但在认识论和境界论意义上,“心与理一”是心学与理学家共同信守的基本理念和终极关怀。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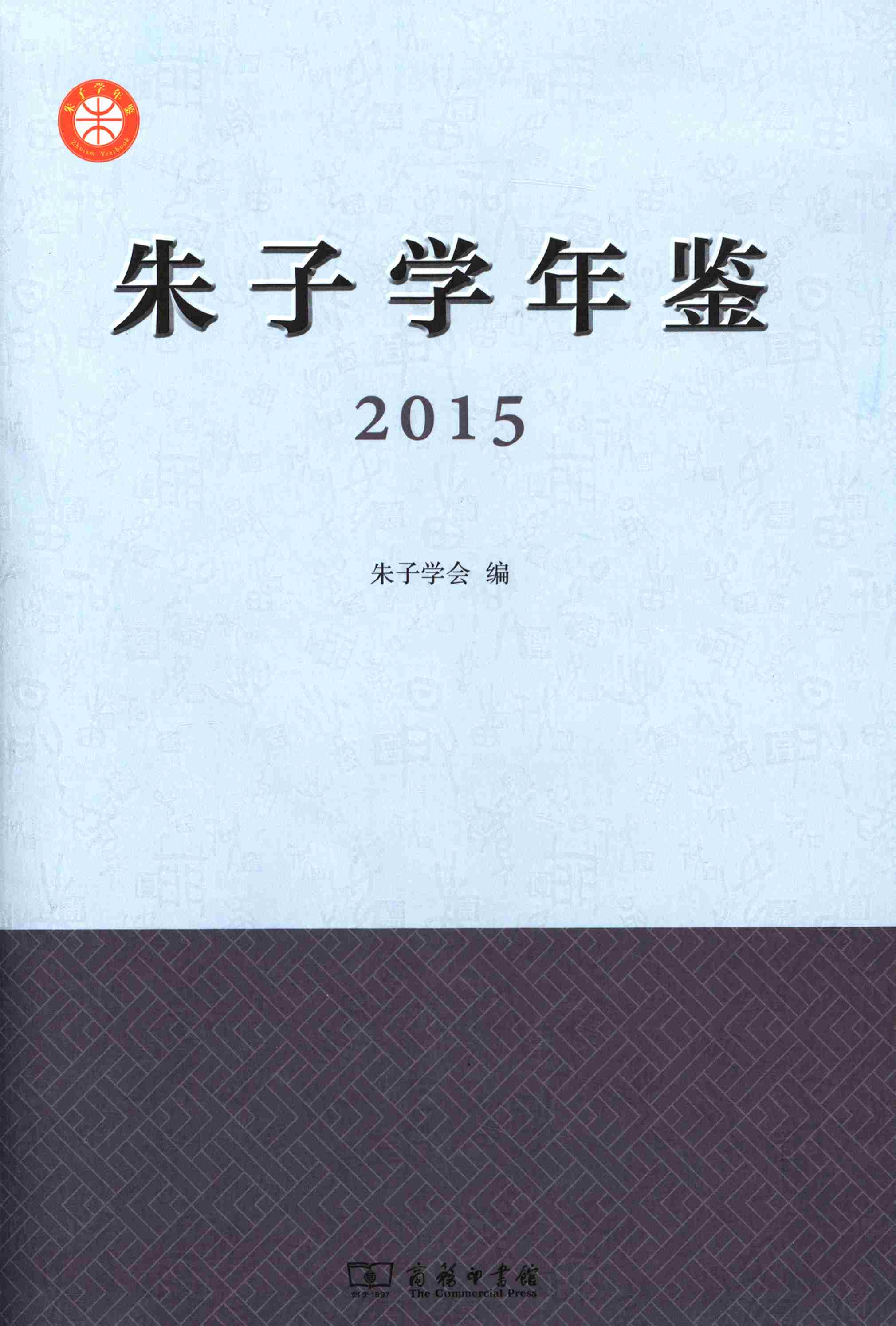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
相关人物
朱人求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