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思有觉、圣凡体别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13 |
| 颗粒名称: | 无思有觉、圣凡体别 |
| 其他题名: | 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8 |
| 页码: | 45-62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朱子心性论中的"中"和"和"概念,以及与"未发"和"已发"相关联的问题。在《中庸》中,“中”指喜怒哀乐未发时的状态,而“和”指喜怒哀乐都处于中正的状态。这两个概念也与心理活动的状态或阶段相关联。朱子学中的“未发”和“已发”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性与情,另一方面指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或阶段。然而,在未发工夫的问题上,不同的理学家意见不一,甚至包括朱子在内的学者个人意见也有变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复杂。本文以朝鲜儒学者李珥的观点为中心,着重分析了他在《圣学辑要》中关于未发问题的论述。栗谷认为,在未发时存在着无思虑但有知觉的状态,他引用了程颐和朱熹的语录,并加入了按语来阐述自己的理解。这些讨论围绕着未发的问题展开,而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未发时是否存在知觉。 |
| 关键词: | 朱子学 思想 探讨 |
内容
前言
《中庸》首章末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提出了“中”“和”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又与“未发”和“发”连在一起,因此,后来宋代新儒家学者在讨论“中和”问题时,也将“未发”和“已发”作为一对独立的范畴加以分析,更由于朱子的加入,“中和”与“未发已发”问题上升为理学最热门的话头之一。在朱子那里,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未发已发”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它们分别指性与情,一是它们分别指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或阶段。[1]这两种含义分别指向理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关于未发工夫,不仅不同的理学家意见不一,乃至像朱子这样的学者,个人意见前后都有变化,使得这一问题十分复杂,也成为今人理解理学工夫论的一个难点。作为朝鲜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的李珥(栗谷,1536~1584),在阐述其儒学思想之时,亦涉及这一议题。了解栗谷对于未发工夫究竟持何观点,不仅对于把握栗谷思想的特质很有必要[2],对于弄清栗谷之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乃至朝鲜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异同,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本文以《圣学辑要》为中心考察栗谷的未发学说,盖栗谷著作虽丰,但与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则是《圣学辑要》一书。该书由五部分构成:统说第一,修己第二,正家第三,为政第四,圣贤道统第五。其中,修己部分最长,又被分成上、中、下三篇,凡十三章。从篇幅上看,“修己”无疑是《圣学辑要》的重点。栗谷为学是典型的程朱进路,伊川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3],栗谷拳拳服膺,“修己”篇的章节安排即充分体现了这一为学顺序:收敛章第三(敬之始)——穷理章第四——正心章第八(敬之终)。正心章详论涵养省察之意,该章前面说涵养,后面说省察。栗谷所说涵养,主要是指静时工夫,属未发范畴[4];而省察则主要是指动时工夫,属已发范畴。在涵养这个部分,栗谷主要选了程颐和朱熹语录,中间加了一段按语。正心章“涵养”一节的选文与按语,构成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栗谷所选诸家语录(包括按语所引),计有:程子(伊川)4条,朱子6条,真德秀(西山)1条,其学问门径及其对朱子的重视,一览无遗。栗谷所加按语,依其内容,可以分为4条:第1条论未发时无思虑而知觉不昧,第2条论未发时有无见闻,第3条论常人与圣贤未发之中之同异,第4条论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属未发工夫还是已发工夫。不难看出,这些按语都紧紧围绕未发问题展开,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尽在其中,而其关键则是未发时到底有无知觉。
1.未发之时,此心寂然,固无一毫思虑。但寂然之中,知觉不昧,有如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也。此处极难理会,但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据此可知,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包含两个要点:首先,未发时无思(毫无思虑);其次,未发时有觉(知觉不昧)。不难看出,这两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按照平常的理解,知觉与思虑很难分开。对于栗谷之说,很容易提出如下疑问:既然知觉不昧,也就是说,人有清醒的知觉,如何又能做到无一毫思虑?难道思虑不属于知觉?如果思虑不属于知觉,那么,栗谷所说的知觉又是指什么?
一、无思有觉
栗谷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要理解他所说的这两点,存在很大的困难,所谓“此处极难理会”。因此他建议,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敬守此心”即可。如果将栗谷此说与程颐答苏昞(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章做一对照,不难发现二者相似之处:
或曰:“先生(按:程颐)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一作最)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202页)
此节讨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究竟属动还是静,程颐先是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大概他自己也感到这个回答可能让人无可措手,遂告诉对方还是先去理会“敬”。栗谷在处理未发问题时,几乎照搬了伊川的教法。事实上,栗谷在选文中就收了伊川这一条材料。[5]
然而,在解释“敬以涵养”的具体方法(术)时,栗谷又回到未发的两个要点上来:“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看来,不弄清无思(思虑、念虑)有觉(知觉不昧、无少昏昧)的确切含义,也无法去做“敬以涵养”的工夫。
看下面这段话,栗谷所说的知觉似乎主要指见闻这类感觉。
2.或问:“未发时亦有见闻乎?”臣(按:栗谷自称)答曰:“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矣。若物之过乎目者,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过乎耳者,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虽有见闻,不作思惟,则不害其为未发也。故程子曰‘目须见,耳须闻’,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以此观之,未发时亦有见闻矣。”(《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虽然问者没有直接就“未发时是否有知觉?”来请教,但“未发时是否有见闻?”这个问题与未发时思虑知觉的讨论显然相关。问者似乎困惑于“未发时亦有见闻”这样的说法,言下之意:有所见闻不就意味着已发吗?
栗谷了解问者心中之疑,所以一上来就说:在一般情况下,见物闻声往往会随之产生念虑,这当然属于已发状态。但他接着又指出,并不是所有闻见都一定会伴随着念虑,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物过乎目,人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物过乎耳,人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总之,虽有见闻,但人不作思惟。按照栗谷,这种情况应当被承认为未发。换句话说,不是有闻见就一定属于已发。在未发状态下,人一样可以有所闻见。这样,有无闻见这一点不应当被用来区分已发未发,有无思惟才是关键。那么,栗谷所说的“思惟”,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这句话来看,“思惟”是指伴随所见所闻而起念。而从“不起见之之心”“不起闻之之心”这些话来看,“思惟”又似乎是指有目的或计划性的意识活动。如果说前者是起念于闻见之后,那么,后者就是起意于闻见之前。相应的,“不作思惟”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有所闻见,但在头脑(内心)没有激起任何联想、情感、欲求;另一种是没有打算闻见或没有任何闻见的冲动而被动地闻见。[6]
以上是分析的说法,在栗谷本人那里可能没有这样的自觉。对他而言,无论是起念还是着意,都代表着一种自我控制或决定的意向性活动,既不同于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反应,也不同于闻、见这样的主要与身(与心相对)相连的感觉或认知行为,后两种精神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不受自我控制或决定,俗语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有以形容之。
关于自我控制的意向性活动与情感反应和具身性认知活动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说明。通常,只要眼睛是睁着的,只要视力正常,当眼前出现一片樱花,人就会看到,得到感官方面的印象:好漂亮的樱花。这个行为不需要主体意志(will)参与其中,无关于意志或意向。春天看到樱花盛开,觉得赏心悦目,乃至流连忘返,这种情感反应也不是出于主体有意而为。但是,是留在书房里完成论文还是去公园赏花,这些行为则是由主体决断的。栗谷说的思惟,更多是主体决断的意志或意向活动。强调未发时有见闻,无非是想对闻见这类比较简单的感觉或知觉活动与思考、意欲这类相对复杂的理智、情感活动做出区分。就提出已发未发概念的《中庸》本文来说,未发主要是与喜怒哀乐等情感或情绪反应连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庸》并没有说“未发时感觉器官处于沉睡状态”,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作者,本来不会产生未发时有无见闻知觉这样的问题。那么,未发有无见闻知觉,是何时以及怎样变成了一个问题呢?历史地看,这是程颐、朱熹这些宋代理学家努力的结果。[7]事实上,栗谷这段话就提到了程、朱各一条语录。它再次显示,栗谷有关未发的看法是以程朱为旨归的。下面,我们就逐一参详。
2.1目须见,耳须闻。(程颐)
这句话出自伊川答苏季明问后章第11节[8],栗谷在选文中对原文做了具录:
(程子语录3)或曰:“当静坐时,物之过乎前者,还见不见?”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也。若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关于静坐时是否有见闻,伊川给了一个语境主义的回答:“看事如何”,有大事时(比如祭祀)无所见亦无所闻,而无事时则有所见亦有所闻。何以有此不同?伊川没有解释。此节与同章第3节可共看,后者亦是关于未发之前(当中之时)有无见闻的问答,其文如下:
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
如同之前有关动静的回答一样,伊川有关闻见的这个回答,亦有试图照顾两边的特点:一方面肯定目无见耳无闻,另一方面也提示见闻之理仍在。
将第3节与第11节对照,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按第3节,静时(当中之时)无见闻;按第11节,静时(无事时)有见闻。静时到底有无见闻?伊川的说法应以哪一个为准?又或者,伊川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朱子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耳有闻目有见。
如耳无闻目无见之答,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其误必矣。盖未发之时,但为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见,耳之有闻,则当愈益精明而不可乱,岂若心不在焉,而遂废耳目之用哉?(《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可见朱子是以第11节的说法为准,准确地说,是以第11节后半截“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为准。伊川关于“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的说法在朱子看来是错误的。
但其(按伊川)曰“当祭祀时,无所见闻”,则古人之制祭服而设旒黈,虽曰欲其不得广视杂听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为真足以全蔽其聪明,使之一无见闻也。若曰履之有绚,以为行戒;尊之有禁,以为酒戒,然初未尝以是而遂不行不饮也。若使当祭之时,真为旒黈所塞,遂如聋瞽,则是礼容乐节,皆不能知,亦将何以致其诚意,而交于鬼神哉?程子之言,决不如是之过也。(《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按此分析,伊川答苏季明问的这条记录还存在失真问题。[9]总体上,朱子对伊川答苏季明之后章评价甚低:“程子备矣,但其答苏季明之后章,记录多失本真,答问不相对值”[10],“大抵此条最多谬误,盖听他人之问,而从旁窃记,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问者之情,是以致此乱道而误人耳。”(《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61~562页)[1]
朱子之所以坚持未发时亦有见闻,在哲学上,是基于他对两组概念所做的区分:心之知、耳之闻、目之见是一组,心之思、耳之听、目之视是一组。前者属未发,后者属已发。
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虽未发而未尝无;心之有思乃与耳之有听、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一有此则不得未发。故程子以有思为已发则可,而记者以无见无闻为未发则不可。若苦未信,则请更以程子之言证之。如称许渤为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尝有如此圣人?[12]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为非,此言皆何谓邪?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答吕子约第三十九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3页)
朱子对思、听、视的用法与一般无异,都是以之为动词,表示认识活动意。但朱子对知、闻、见的用法与一般则不同,一般是以之为认识的结果或内容,而朱子则以之为认识的能力。通常,人们会说:思而不知(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表示:真正的认识活动必须有意识(consciousness)参与其中,否则,就会出现没有结果的认识活动。朱子为了合于未发已发的规定,故于思、听、视不取活动义,而取能力义。实际上,准确表达朱子意思的词应该是:思考力、听力、视力,而不是:思、听、视。朱子所说的“有知觉”或“知觉不昧”,正是说认识能力或潜能,而不是说认识活动或认识结果。在未发的状态下,当然不能说有知、闻、见,但可以说有思考力、听力、视力。如果朱子只是强调未发状态下,心体的明觉不曾失去,这当然是不错的。就像以镜为喻:镜未照物,不妨其有光明(即能照之功),但不能说其中有影(所照之物影)。但是,当朱子说未发时有见有闻,在语义上就存在歧义,人们会以为是在说有所见有所闻(事实上,朱子本人有时就是这样用的,比如,他在上引这段话里就说“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这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如果没有有意识地去认识(思、听、视),何谈认识的结果或内容(知、闻、见)?而按伊川之见,有思即是已发[13,那么,有所见有所闻又如何还能说是未发呢?
这里的问题出在“思”上。由于伊川并没有规定“思”特指分散心神,使其不专一的“闲思杂虑”,人们当然可以将其广义地理解为所有的知觉活动。事实上,伊川本人有时也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伊川了解,他所说的“思”或“知觉”乃是特指产生使人从所从事的活动当中分散注意力的思虑、念头,再宣称“才思便是已发”或“才知觉便是已发”,就没有问题了。如此看来,未发已发成为问题,纠缠不清,是程朱(尤其是伊川)等人理解的问题,而非《中庸》本文的问题,因为,对《中庸》来说,它明明是讲喜怒哀乐之情的发动与否,而不是对所有知觉活动而言。[14]《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主要是指人心没有生出私心杂念,而并不是说心无知觉。
综观程、朱之说,无论是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还是关于未发时究竟属动还是静,其陈述都存在不能自洽和难以服人之处。栗谷采纳了经过朱子裁断的未发时亦有见闻之说,但从他在选取伊川论未发的语录时依然收入朱子批评甚烈的那条材料这一点来看,伊川之说的内在矛盾以及朱子对伊川的批评与修正,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二、圣凡体别
为驳斥以未有见闻为未发的观点,朱子更发展出一种未发之体上的圣凡区别说,其大意是:未发之时,普通人或有无见无闻之事,而圣人则决不如此,其心聪明洞彻,闻见不爽。栗谷注意到朱子的这个说法,在按语中做了引用。
2.2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朱熹)
此为朱子《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中语,栗谷所引不全,读者从中难知朱子“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之究竟,兹将上下文一并抄录。
须知上四句分别中和,不是说圣人事,只是泛说道理名色地头如此。下面说“致中和”,方是说做功夫处,而唯圣人为能尽之。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若必如此,则《洪范》五事当云“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乃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费尽工夫,却只养得成一枚痴呆罔两汉矣。
(《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35页)
朱子认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这个叙述才是“说做功夫处”,而且“唯圣人为能尽之”。至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只是解释“中”“和”等名词而已。朱子这样理解“致中和”,是把“致”看成动词,这个解释显然受到了《大学》“致知”一词的影响。而把“致中和”功夫看成只有圣人才能完成,则意味着,被子思认为是“天下之大本”的那个“中”,不是常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就能达到的,而只能是圣人才如此。朱子的这个说法在《中庸》本文当中也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如《中庸》第三十一章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第三十二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不过,朱子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却主要是《尚书·洪范》有关“五事”之说。
《尚书·洪范》提到九类常道(九畴),其中第二类就是所谓“五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指:貌、言、视、听、思。《洪范》作者还进一步规定了这五事所应达到的目标:“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汉]孔安国《尚书》卷七“洪范第六周书”,四部丛刊景宋本)从理论上说,恭、从、明、聪、睿这些性质是应然或规范,并不就是实然。不过,古人有一种倾向,即把这些规范看作主体内在自发的美德追求,孔子把这种自发的美德追求称之为“思”,而有所谓“九思”之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第十六》)[15]《礼记·玉藻》也有对君子容貌方面的要求,提出所谓“九容”之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礼记·玉藻第十三》)可以设想,一个君子经过长期修养,他在视听方面自然会达到聪、明之境,而其一举手一投足,也会给人以恭重之感。
从《洪范》本文看,貌、言、视、听、思这五事是各自独立的,但郑玄(127~200)在解释“睿作圣”时,认为“睿”是“通”的意思,还根据孔子说的“圣者,通也,兼四而明”把“圣”解释为“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16],从而,由“思”出发而达到的“圣”就变成了兼包貌、言、视、听四者的更高范畴。易言之,如果一个人通过“思”达到“圣”的境界,那么,他同时也就兼具了貌之恭、言之从、视之明、听之聪。合起来,就是:圣人聪明睿知。“聪明”是就耳目闻见这些感觉或知觉能力而言,本来并不是形容睿智(知)这样的理性能力,现在,经过学者诠释,《洪范》以及《中庸》当中包含了“圣人聪明睿知”这样的命题,就这样,原本形容感觉或知觉能力的聪明与形容理性能力的睿智很自然地结合到一起,并且,它们都统一在“圣”的名义之下。
对于这种聪明睿知的圣人,自然可以说其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其听也聪,其视也明,亦即:即便与事物没有接触,其听之聪、视之明也不会消失。说未发时无见无闻,对于这样的圣人自然不适用。
伊川与苏季明讨论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的问题时,只是一概而论,还没有像朱子这样把常人与圣人分开来说。按照朱子,关于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准确的回答应该是:未发状态下,圣人有见有闻。至此,朱子实际上已对未发状态下“目须见,耳须闻”的说法做了一定的修正,相对于之前他就伊川答苏季明问所做的裁决——未发时,耳有闻目有见,现在这个说法在辞气上已经减弱很多。
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朱子观点的不同版本,都为栗谷所继承。如前所述,栗谷接受了“目须见耳须闻”之说,现在,他也赞成朱子的“圣人未发时有见有闻”论。
3.又问:“常人之心固有未发时矣,其中体亦与圣贤之未发无别耶?”臣(按:栗谷)答曰:“常人无涵养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则乱,中体不立。幸于须臾之顷,不昏不乱,则其未发之中,亦与圣贤无别。但未久而或颓放,或胶扰,旋失其本体,则霎时之中,安能救终日之昏乱以立大本乎?”(《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12页)
在朱子那里,“圣人与常人,其未发之中体是否有别?”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以明晰的方式提出,朱子只是强调,《中庸》所说的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唯有圣人才能如此,至于常人未发之中是如何,朱子则语焉不详。[17]而在栗谷这里,问题已经被尖锐地摆到面前,令他无法回避。栗谷的回答,是“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的一个较强版本。
依栗谷,没有做过涵养省察功夫的常人,其心不昏则乱,因此,其未发之中,与圣人(圣贤)有别。栗谷也提到,常人之心在某些时刻,也许不昏不乱,从而,其未发之中与圣贤无别,但这种时刻稍瞬即逝,总之,都难以担当《中庸》所说的“立天下之大本”的重任。
栗谷关于常人与圣人未发之同异的讨论,其核心涉及如何认识《中庸》所说的“中”。这个“中”,《中庸》既说它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又说它是“天下之大本”。就前一个说法而言,“中”是一个中性描述,只要符合“喜怒哀乐”未萌这个条件,任何人的心,这个时候都可以说是“中”。然而,就后一个说法而言,“中”就变成了价值源泉,从而,再不能说,任何人的心,都可以作为人类的价值源泉。合理的解释,只能像朱子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大本)的,是圣人未发之中。
吕大临(与叔)曾经把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理解为“未发之中”,结果被程颐讥为“不识大本”。伊川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认定赤子之心属已发,而《中庸》所说的“大本”是指“未发之中”。吕大临则为自己辩解说,孟子意义上的赤子之心正是指未发之际而言的,其特点是无所偏倚,完全符合“未发之中”的要求。[18]吕大临在申述时,也谈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同异的问题。
圣人智周万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岂非止取纯一无伪,可与圣人同乎?非谓无毫发之异也。(《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7页)
吕大临承认,赤子与圣人之心有所差异,但他坚持认为,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正是就其与圣人相同而言的。按照吕大临的理解,孟子所说的“纯一无伪”的赤子之心,是指其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易言之,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在其未发时无不同。
朱子在评论程颐答吕大临论中书时,一方面肯定了程颐关于赤子之心不是中而未远乎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对吕大临关于赤子之心属未发的说法也给予了一定的承认。
问:“赤子之心,指已发而言,然亦有未发时。”曰:“亦有未发时,但孟子所论,乃指其已发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无那赤子时
心。”(义刚)(《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问:“赤子之心,莫是发而未远乎中,不可作未发时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发时,也有已发时。今欲将赤子之心专作已发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但其已发未有私欲,故未远乎中耳。”(铢)(《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与伊川一口断定赤子之心指已发的立场相比,朱子的看法显得更为圆融。而关于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之同异,朱子的观点与吕大临也更为接近,因为他说:“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然而,如此一来,朱子关于“常人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之同异”的看法就显出其复杂的一面。
朱子这种“一同”论亦见于另一条材料。
……又问:“‘赤子之心’处,此是一篇大节目。程先生云:‘毫厘有异,得为大本乎?’看吕氏此处不特毫厘差,乃大段差。然毫厘差亦不得。圣
人之心如明镜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论圣人,与叔之失,却是认赤子之已发者皆为未发。”曰:“固是如此,然若论未发时,众人心亦不可与圣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天理别在一处去了。”曰:“如此说,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大抵此书答辞,亦有反为所窘处。当初不若只与论圣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则自分明。”(可学)(《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第2504页)
朱子不同意说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不同,可能主要是基于“性即理”的观念。[19]不过,朱子在对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相同做肯定陈述时,语气并不那么强烈,而是表现出某种审慎:“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如果说众人或常人未发时心多扰扰,那当然不能说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同。按照这个表述,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之心不同的概率要大于相同。栗谷关于圣人与常人未发之体有别还是无别的论述,在思路甚至个别用词上,都与朱子的这个表述有相似之处。有理由相信,栗谷之说是从朱子这里出去。
栗谷论未发的最后一条按语是关于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之说的评论。
4.又问:“延平先生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作何气象,朱子曰‘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此说何如?”臣(按:栗谷)答曰:“才有所
思,便是已发。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故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2页)
“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是朱子评其师李延平之教的话,语出《答何叔京第二书》: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答何叔京第二书》,《文集》卷四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此书写作年月,据陈来考证,当乾道二年丙戌(1166)。[20]时朱子37岁,即丙戌之悟“中和旧说”之际,上距延平之殁(隆兴元年癸未,1163)三载。
栗谷提到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见《语类》卷一百三: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3~2604页)
按:朱子这里所说,只是自悔旧日[21]为李先生撰《行状》时下得语重,并没有点出“以体认字下得重”,盖《行状》原文为“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并无“体认”二字。“以体认字下得重”是栗谷自己的理解。包括前面所说的“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其根据应当都是下面这条语录。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
观时恁著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不观观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4页)
朱子自述,对延平之教以伊川之语格之。这里提到的伊川语,还有栗谷所说的“才有所思,即是已发”,都是出自以下这条语录:
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页)
伊川正确地指出,“求中”之“求”含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计划性在里面,即是“思量”(思),而“既思,即是已发”。所以,“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旦存了求的念头,就不再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状态,而变成已发状态了。对于延平之教,乃至整个龟山门下指诀,朱子的不满,不只是其在名义上说不通,更认为其有所偏。所谓偏,是指这种工夫过于偏向静而忽略了动。朱子认为,伊川的持敬之学相比之下就要中正平和得多。
……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
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596~2597页)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
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却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2页)
问:伊川答苏季明云:“求中于喜怒哀乐,却是已发”。某观延平亦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为如何,此说又似与季明同。曰:但欲见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道,则流于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朱子语类》卷九十六,第2468页)
按照“既思即是已发”的观点,未发时做工夫几乎不可能,因为一有所念,就已经脱离未发状态。程、朱把体验、体认乃至观都理解为思量、思维,不能不说,这种解释太过偏于理性主义,道南一脉,尤其是延平,静中观未发气象,恰恰是以消除目的性或功利性念头(去念,融释)为特征的一种功夫。其日常修炼,以达到内心摆脱一切计较考虑的澄心为效验。
无疑,栗谷是程朱持敬之学的信奉者,以“观(体认、体验)未发时气象”为教法的延平乃至道南一脉的工夫论,与之终不相契,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栗谷对实践未发工夫的延平之教亦保有一份同情,要求“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然而,何谓“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它与延平所说的“静中观未发气象”区别究竟何在?文献不足,不敢妄议。
结语
本文通过评述栗谷在《圣学辑要》“涵养”一节所加的按语,对栗谷有关未发的思想做了分析,具体揭示了他对程、朱之教尤其是朱子观点的继承。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处理对栗谷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富于争议的“四七”之辩的内容,尤其是栗谷有关人心道心或气质变化的思想对其未发之说的影响。囿于语言,笔者对韩国学界丰富的栗谷研究成果虽然很感兴趣却也无法吸收。因此,关于栗谷的未发思想,本文所做,应当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仅就笔者现有的考察来看,说栗谷之学是纯粹的朱子学路数,绝无可疑。栗谷作为一个朝鲜儒者,他对朱子学的熟稔程度,令身为中国学人的笔者感到吃惊,发自内心地表示敬佩。当然,笔者在肯定栗谷对程朱之学的认识与奉持的同时,也指出,栗谷对程朱理论的某些内部矛盾及其学说存在的病痛,似乎还缺乏明确的意识与进一步的讨论。总体上,就有关未发的思想来看,栗谷对朱子学,给笔者的印象是,继承有余,而开发不足。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中庸》首章末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提出了“中”“和”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又与“未发”和“发”连在一起,因此,后来宋代新儒家学者在讨论“中和”问题时,也将“未发”和“已发”作为一对独立的范畴加以分析,更由于朱子的加入,“中和”与“未发已发”问题上升为理学最热门的话头之一。在朱子那里,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未发已发”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它们分别指性与情,一是它们分别指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或阶段。[1]这两种含义分别指向理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关于未发工夫,不仅不同的理学家意见不一,乃至像朱子这样的学者,个人意见前后都有变化,使得这一问题十分复杂,也成为今人理解理学工夫论的一个难点。作为朝鲜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的李珥(栗谷,1536~1584),在阐述其儒学思想之时,亦涉及这一议题。了解栗谷对于未发工夫究竟持何观点,不仅对于把握栗谷思想的特质很有必要[2],对于弄清栗谷之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乃至朝鲜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异同,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本文以《圣学辑要》为中心考察栗谷的未发学说,盖栗谷著作虽丰,但与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则是《圣学辑要》一书。该书由五部分构成:统说第一,修己第二,正家第三,为政第四,圣贤道统第五。其中,修己部分最长,又被分成上、中、下三篇,凡十三章。从篇幅上看,“修己”无疑是《圣学辑要》的重点。栗谷为学是典型的程朱进路,伊川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3],栗谷拳拳服膺,“修己”篇的章节安排即充分体现了这一为学顺序:收敛章第三(敬之始)——穷理章第四——正心章第八(敬之终)。正心章详论涵养省察之意,该章前面说涵养,后面说省察。栗谷所说涵养,主要是指静时工夫,属未发范畴[4];而省察则主要是指动时工夫,属已发范畴。在涵养这个部分,栗谷主要选了程颐和朱熹语录,中间加了一段按语。正心章“涵养”一节的选文与按语,构成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栗谷所选诸家语录(包括按语所引),计有:程子(伊川)4条,朱子6条,真德秀(西山)1条,其学问门径及其对朱子的重视,一览无遗。栗谷所加按语,依其内容,可以分为4条:第1条论未发时无思虑而知觉不昧,第2条论未发时有无见闻,第3条论常人与圣贤未发之中之同异,第4条论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属未发工夫还是已发工夫。不难看出,这些按语都紧紧围绕未发问题展开,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尽在其中,而其关键则是未发时到底有无知觉。
1.未发之时,此心寂然,固无一毫思虑。但寂然之中,知觉不昧,有如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也。此处极难理会,但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据此可知,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包含两个要点:首先,未发时无思(毫无思虑);其次,未发时有觉(知觉不昧)。不难看出,这两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按照平常的理解,知觉与思虑很难分开。对于栗谷之说,很容易提出如下疑问:既然知觉不昧,也就是说,人有清醒的知觉,如何又能做到无一毫思虑?难道思虑不属于知觉?如果思虑不属于知觉,那么,栗谷所说的知觉又是指什么?
一、无思有觉
栗谷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要理解他所说的这两点,存在很大的困难,所谓“此处极难理会”。因此他建议,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敬守此心”即可。如果将栗谷此说与程颐答苏昞(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章做一对照,不难发现二者相似之处:
或曰:“先生(按:程颐)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一作最)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202页)
此节讨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究竟属动还是静,程颐先是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大概他自己也感到这个回答可能让人无可措手,遂告诉对方还是先去理会“敬”。栗谷在处理未发问题时,几乎照搬了伊川的教法。事实上,栗谷在选文中就收了伊川这一条材料。[5]
然而,在解释“敬以涵养”的具体方法(术)时,栗谷又回到未发的两个要点上来:“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看来,不弄清无思(思虑、念虑)有觉(知觉不昧、无少昏昧)的确切含义,也无法去做“敬以涵养”的工夫。
看下面这段话,栗谷所说的知觉似乎主要指见闻这类感觉。
2.或问:“未发时亦有见闻乎?”臣(按:栗谷自称)答曰:“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矣。若物之过乎目者,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过乎耳者,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虽有见闻,不作思惟,则不害其为未发也。故程子曰‘目须见,耳须闻’,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以此观之,未发时亦有见闻矣。”(《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虽然问者没有直接就“未发时是否有知觉?”来请教,但“未发时是否有见闻?”这个问题与未发时思虑知觉的讨论显然相关。问者似乎困惑于“未发时亦有见闻”这样的说法,言下之意:有所见闻不就意味着已发吗?
栗谷了解问者心中之疑,所以一上来就说:在一般情况下,见物闻声往往会随之产生念虑,这当然属于已发状态。但他接着又指出,并不是所有闻见都一定会伴随着念虑,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物过乎目,人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物过乎耳,人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总之,虽有见闻,但人不作思惟。按照栗谷,这种情况应当被承认为未发。换句话说,不是有闻见就一定属于已发。在未发状态下,人一样可以有所闻见。这样,有无闻见这一点不应当被用来区分已发未发,有无思惟才是关键。那么,栗谷所说的“思惟”,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这句话来看,“思惟”是指伴随所见所闻而起念。而从“不起见之之心”“不起闻之之心”这些话来看,“思惟”又似乎是指有目的或计划性的意识活动。如果说前者是起念于闻见之后,那么,后者就是起意于闻见之前。相应的,“不作思惟”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有所闻见,但在头脑(内心)没有激起任何联想、情感、欲求;另一种是没有打算闻见或没有任何闻见的冲动而被动地闻见。[6]
以上是分析的说法,在栗谷本人那里可能没有这样的自觉。对他而言,无论是起念还是着意,都代表着一种自我控制或决定的意向性活动,既不同于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反应,也不同于闻、见这样的主要与身(与心相对)相连的感觉或认知行为,后两种精神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不受自我控制或决定,俗语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有以形容之。
关于自我控制的意向性活动与情感反应和具身性认知活动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说明。通常,只要眼睛是睁着的,只要视力正常,当眼前出现一片樱花,人就会看到,得到感官方面的印象:好漂亮的樱花。这个行为不需要主体意志(will)参与其中,无关于意志或意向。春天看到樱花盛开,觉得赏心悦目,乃至流连忘返,这种情感反应也不是出于主体有意而为。但是,是留在书房里完成论文还是去公园赏花,这些行为则是由主体决断的。栗谷说的思惟,更多是主体决断的意志或意向活动。强调未发时有见闻,无非是想对闻见这类比较简单的感觉或知觉活动与思考、意欲这类相对复杂的理智、情感活动做出区分。就提出已发未发概念的《中庸》本文来说,未发主要是与喜怒哀乐等情感或情绪反应连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庸》并没有说“未发时感觉器官处于沉睡状态”,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作者,本来不会产生未发时有无见闻知觉这样的问题。那么,未发有无见闻知觉,是何时以及怎样变成了一个问题呢?历史地看,这是程颐、朱熹这些宋代理学家努力的结果。[7]事实上,栗谷这段话就提到了程、朱各一条语录。它再次显示,栗谷有关未发的看法是以程朱为旨归的。下面,我们就逐一参详。
2.1目须见,耳须闻。(程颐)
这句话出自伊川答苏季明问后章第11节[8],栗谷在选文中对原文做了具录:
(程子语录3)或曰:“当静坐时,物之过乎前者,还见不见?”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也。若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关于静坐时是否有见闻,伊川给了一个语境主义的回答:“看事如何”,有大事时(比如祭祀)无所见亦无所闻,而无事时则有所见亦有所闻。何以有此不同?伊川没有解释。此节与同章第3节可共看,后者亦是关于未发之前(当中之时)有无见闻的问答,其文如下:
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
如同之前有关动静的回答一样,伊川有关闻见的这个回答,亦有试图照顾两边的特点:一方面肯定目无见耳无闻,另一方面也提示见闻之理仍在。
将第3节与第11节对照,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按第3节,静时(当中之时)无见闻;按第11节,静时(无事时)有见闻。静时到底有无见闻?伊川的说法应以哪一个为准?又或者,伊川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朱子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耳有闻目有见。
如耳无闻目无见之答,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其误必矣。盖未发之时,但为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见,耳之有闻,则当愈益精明而不可乱,岂若心不在焉,而遂废耳目之用哉?(《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可见朱子是以第11节的说法为准,准确地说,是以第11节后半截“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为准。伊川关于“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的说法在朱子看来是错误的。
但其(按伊川)曰“当祭祀时,无所见闻”,则古人之制祭服而设旒黈,虽曰欲其不得广视杂听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为真足以全蔽其聪明,使之一无见闻也。若曰履之有绚,以为行戒;尊之有禁,以为酒戒,然初未尝以是而遂不行不饮也。若使当祭之时,真为旒黈所塞,遂如聋瞽,则是礼容乐节,皆不能知,亦将何以致其诚意,而交于鬼神哉?程子之言,决不如是之过也。(《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按此分析,伊川答苏季明问的这条记录还存在失真问题。[9]总体上,朱子对伊川答苏季明之后章评价甚低:“程子备矣,但其答苏季明之后章,记录多失本真,答问不相对值”[10],“大抵此条最多谬误,盖听他人之问,而从旁窃记,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问者之情,是以致此乱道而误人耳。”(《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61~562页)[1]
朱子之所以坚持未发时亦有见闻,在哲学上,是基于他对两组概念所做的区分:心之知、耳之闻、目之见是一组,心之思、耳之听、目之视是一组。前者属未发,后者属已发。
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虽未发而未尝无;心之有思乃与耳之有听、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一有此则不得未发。故程子以有思为已发则可,而记者以无见无闻为未发则不可。若苦未信,则请更以程子之言证之。如称许渤为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尝有如此圣人?[12]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为非,此言皆何谓邪?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答吕子约第三十九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3页)
朱子对思、听、视的用法与一般无异,都是以之为动词,表示认识活动意。但朱子对知、闻、见的用法与一般则不同,一般是以之为认识的结果或内容,而朱子则以之为认识的能力。通常,人们会说:思而不知(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表示:真正的认识活动必须有意识(consciousness)参与其中,否则,就会出现没有结果的认识活动。朱子为了合于未发已发的规定,故于思、听、视不取活动义,而取能力义。实际上,准确表达朱子意思的词应该是:思考力、听力、视力,而不是:思、听、视。朱子所说的“有知觉”或“知觉不昧”,正是说认识能力或潜能,而不是说认识活动或认识结果。在未发的状态下,当然不能说有知、闻、见,但可以说有思考力、听力、视力。如果朱子只是强调未发状态下,心体的明觉不曾失去,这当然是不错的。就像以镜为喻:镜未照物,不妨其有光明(即能照之功),但不能说其中有影(所照之物影)。但是,当朱子说未发时有见有闻,在语义上就存在歧义,人们会以为是在说有所见有所闻(事实上,朱子本人有时就是这样用的,比如,他在上引这段话里就说“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这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如果没有有意识地去认识(思、听、视),何谈认识的结果或内容(知、闻、见)?而按伊川之见,有思即是已发[13,那么,有所见有所闻又如何还能说是未发呢?
这里的问题出在“思”上。由于伊川并没有规定“思”特指分散心神,使其不专一的“闲思杂虑”,人们当然可以将其广义地理解为所有的知觉活动。事实上,伊川本人有时也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伊川了解,他所说的“思”或“知觉”乃是特指产生使人从所从事的活动当中分散注意力的思虑、念头,再宣称“才思便是已发”或“才知觉便是已发”,就没有问题了。如此看来,未发已发成为问题,纠缠不清,是程朱(尤其是伊川)等人理解的问题,而非《中庸》本文的问题,因为,对《中庸》来说,它明明是讲喜怒哀乐之情的发动与否,而不是对所有知觉活动而言。[14]《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主要是指人心没有生出私心杂念,而并不是说心无知觉。
综观程、朱之说,无论是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还是关于未发时究竟属动还是静,其陈述都存在不能自洽和难以服人之处。栗谷采纳了经过朱子裁断的未发时亦有见闻之说,但从他在选取伊川论未发的语录时依然收入朱子批评甚烈的那条材料这一点来看,伊川之说的内在矛盾以及朱子对伊川的批评与修正,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二、圣凡体别
为驳斥以未有见闻为未发的观点,朱子更发展出一种未发之体上的圣凡区别说,其大意是:未发之时,普通人或有无见无闻之事,而圣人则决不如此,其心聪明洞彻,闻见不爽。栗谷注意到朱子的这个说法,在按语中做了引用。
2.2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朱熹)
此为朱子《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中语,栗谷所引不全,读者从中难知朱子“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之究竟,兹将上下文一并抄录。
须知上四句分别中和,不是说圣人事,只是泛说道理名色地头如此。下面说“致中和”,方是说做功夫处,而唯圣人为能尽之。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若必如此,则《洪范》五事当云“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乃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费尽工夫,却只养得成一枚痴呆罔两汉矣。
(《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35页)
朱子认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这个叙述才是“说做功夫处”,而且“唯圣人为能尽之”。至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只是解释“中”“和”等名词而已。朱子这样理解“致中和”,是把“致”看成动词,这个解释显然受到了《大学》“致知”一词的影响。而把“致中和”功夫看成只有圣人才能完成,则意味着,被子思认为是“天下之大本”的那个“中”,不是常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就能达到的,而只能是圣人才如此。朱子的这个说法在《中庸》本文当中也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如《中庸》第三十一章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第三十二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不过,朱子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却主要是《尚书·洪范》有关“五事”之说。
《尚书·洪范》提到九类常道(九畴),其中第二类就是所谓“五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指:貌、言、视、听、思。《洪范》作者还进一步规定了这五事所应达到的目标:“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汉]孔安国《尚书》卷七“洪范第六周书”,四部丛刊景宋本)从理论上说,恭、从、明、聪、睿这些性质是应然或规范,并不就是实然。不过,古人有一种倾向,即把这些规范看作主体内在自发的美德追求,孔子把这种自发的美德追求称之为“思”,而有所谓“九思”之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第十六》)[15]《礼记·玉藻》也有对君子容貌方面的要求,提出所谓“九容”之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礼记·玉藻第十三》)可以设想,一个君子经过长期修养,他在视听方面自然会达到聪、明之境,而其一举手一投足,也会给人以恭重之感。
从《洪范》本文看,貌、言、视、听、思这五事是各自独立的,但郑玄(127~200)在解释“睿作圣”时,认为“睿”是“通”的意思,还根据孔子说的“圣者,通也,兼四而明”把“圣”解释为“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16],从而,由“思”出发而达到的“圣”就变成了兼包貌、言、视、听四者的更高范畴。易言之,如果一个人通过“思”达到“圣”的境界,那么,他同时也就兼具了貌之恭、言之从、视之明、听之聪。合起来,就是:圣人聪明睿知。“聪明”是就耳目闻见这些感觉或知觉能力而言,本来并不是形容睿智(知)这样的理性能力,现在,经过学者诠释,《洪范》以及《中庸》当中包含了“圣人聪明睿知”这样的命题,就这样,原本形容感觉或知觉能力的聪明与形容理性能力的睿智很自然地结合到一起,并且,它们都统一在“圣”的名义之下。
对于这种聪明睿知的圣人,自然可以说其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其听也聪,其视也明,亦即:即便与事物没有接触,其听之聪、视之明也不会消失。说未发时无见无闻,对于这样的圣人自然不适用。
伊川与苏季明讨论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的问题时,只是一概而论,还没有像朱子这样把常人与圣人分开来说。按照朱子,关于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准确的回答应该是:未发状态下,圣人有见有闻。至此,朱子实际上已对未发状态下“目须见,耳须闻”的说法做了一定的修正,相对于之前他就伊川答苏季明问所做的裁决——未发时,耳有闻目有见,现在这个说法在辞气上已经减弱很多。
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朱子观点的不同版本,都为栗谷所继承。如前所述,栗谷接受了“目须见耳须闻”之说,现在,他也赞成朱子的“圣人未发时有见有闻”论。
3.又问:“常人之心固有未发时矣,其中体亦与圣贤之未发无别耶?”臣(按:栗谷)答曰:“常人无涵养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则乱,中体不立。幸于须臾之顷,不昏不乱,则其未发之中,亦与圣贤无别。但未久而或颓放,或胶扰,旋失其本体,则霎时之中,安能救终日之昏乱以立大本乎?”(《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12页)
在朱子那里,“圣人与常人,其未发之中体是否有别?”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以明晰的方式提出,朱子只是强调,《中庸》所说的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唯有圣人才能如此,至于常人未发之中是如何,朱子则语焉不详。[17]而在栗谷这里,问题已经被尖锐地摆到面前,令他无法回避。栗谷的回答,是“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的一个较强版本。
依栗谷,没有做过涵养省察功夫的常人,其心不昏则乱,因此,其未发之中,与圣人(圣贤)有别。栗谷也提到,常人之心在某些时刻,也许不昏不乱,从而,其未发之中与圣贤无别,但这种时刻稍瞬即逝,总之,都难以担当《中庸》所说的“立天下之大本”的重任。
栗谷关于常人与圣人未发之同异的讨论,其核心涉及如何认识《中庸》所说的“中”。这个“中”,《中庸》既说它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又说它是“天下之大本”。就前一个说法而言,“中”是一个中性描述,只要符合“喜怒哀乐”未萌这个条件,任何人的心,这个时候都可以说是“中”。然而,就后一个说法而言,“中”就变成了价值源泉,从而,再不能说,任何人的心,都可以作为人类的价值源泉。合理的解释,只能像朱子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大本)的,是圣人未发之中。
吕大临(与叔)曾经把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理解为“未发之中”,结果被程颐讥为“不识大本”。伊川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认定赤子之心属已发,而《中庸》所说的“大本”是指“未发之中”。吕大临则为自己辩解说,孟子意义上的赤子之心正是指未发之际而言的,其特点是无所偏倚,完全符合“未发之中”的要求。[18]吕大临在申述时,也谈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同异的问题。
圣人智周万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岂非止取纯一无伪,可与圣人同乎?非谓无毫发之异也。(《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7页)
吕大临承认,赤子与圣人之心有所差异,但他坚持认为,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正是就其与圣人相同而言的。按照吕大临的理解,孟子所说的“纯一无伪”的赤子之心,是指其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易言之,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在其未发时无不同。
朱子在评论程颐答吕大临论中书时,一方面肯定了程颐关于赤子之心不是中而未远乎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对吕大临关于赤子之心属未发的说法也给予了一定的承认。
问:“赤子之心,指已发而言,然亦有未发时。”曰:“亦有未发时,但孟子所论,乃指其已发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无那赤子时
心。”(义刚)(《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问:“赤子之心,莫是发而未远乎中,不可作未发时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发时,也有已发时。今欲将赤子之心专作已发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但其已发未有私欲,故未远乎中耳。”(铢)(《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与伊川一口断定赤子之心指已发的立场相比,朱子的看法显得更为圆融。而关于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之同异,朱子的观点与吕大临也更为接近,因为他说:“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然而,如此一来,朱子关于“常人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之同异”的看法就显出其复杂的一面。
朱子这种“一同”论亦见于另一条材料。
……又问:“‘赤子之心’处,此是一篇大节目。程先生云:‘毫厘有异,得为大本乎?’看吕氏此处不特毫厘差,乃大段差。然毫厘差亦不得。圣
人之心如明镜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论圣人,与叔之失,却是认赤子之已发者皆为未发。”曰:“固是如此,然若论未发时,众人心亦不可与圣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天理别在一处去了。”曰:“如此说,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大抵此书答辞,亦有反为所窘处。当初不若只与论圣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则自分明。”(可学)(《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第2504页)
朱子不同意说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不同,可能主要是基于“性即理”的观念。[19]不过,朱子在对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相同做肯定陈述时,语气并不那么强烈,而是表现出某种审慎:“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如果说众人或常人未发时心多扰扰,那当然不能说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同。按照这个表述,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之心不同的概率要大于相同。栗谷关于圣人与常人未发之体有别还是无别的论述,在思路甚至个别用词上,都与朱子的这个表述有相似之处。有理由相信,栗谷之说是从朱子这里出去。
栗谷论未发的最后一条按语是关于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之说的评论。
4.又问:“延平先生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作何气象,朱子曰‘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此说何如?”臣(按:栗谷)答曰:“才有所
思,便是已发。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故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2页)
“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是朱子评其师李延平之教的话,语出《答何叔京第二书》: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答何叔京第二书》,《文集》卷四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此书写作年月,据陈来考证,当乾道二年丙戌(1166)。[20]时朱子37岁,即丙戌之悟“中和旧说”之际,上距延平之殁(隆兴元年癸未,1163)三载。
栗谷提到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见《语类》卷一百三: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3~2604页)
按:朱子这里所说,只是自悔旧日[21]为李先生撰《行状》时下得语重,并没有点出“以体认字下得重”,盖《行状》原文为“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并无“体认”二字。“以体认字下得重”是栗谷自己的理解。包括前面所说的“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其根据应当都是下面这条语录。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
观时恁著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不观观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4页)
朱子自述,对延平之教以伊川之语格之。这里提到的伊川语,还有栗谷所说的“才有所思,即是已发”,都是出自以下这条语录:
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页)
伊川正确地指出,“求中”之“求”含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计划性在里面,即是“思量”(思),而“既思,即是已发”。所以,“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旦存了求的念头,就不再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状态,而变成已发状态了。对于延平之教,乃至整个龟山门下指诀,朱子的不满,不只是其在名义上说不通,更认为其有所偏。所谓偏,是指这种工夫过于偏向静而忽略了动。朱子认为,伊川的持敬之学相比之下就要中正平和得多。
……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
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596~2597页)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
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却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2页)
问:伊川答苏季明云:“求中于喜怒哀乐,却是已发”。某观延平亦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为如何,此说又似与季明同。曰:但欲见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道,则流于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朱子语类》卷九十六,第2468页)
按照“既思即是已发”的观点,未发时做工夫几乎不可能,因为一有所念,就已经脱离未发状态。程、朱把体验、体认乃至观都理解为思量、思维,不能不说,这种解释太过偏于理性主义,道南一脉,尤其是延平,静中观未发气象,恰恰是以消除目的性或功利性念头(去念,融释)为特征的一种功夫。其日常修炼,以达到内心摆脱一切计较考虑的澄心为效验。
无疑,栗谷是程朱持敬之学的信奉者,以“观(体认、体验)未发时气象”为教法的延平乃至道南一脉的工夫论,与之终不相契,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栗谷对实践未发工夫的延平之教亦保有一份同情,要求“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然而,何谓“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它与延平所说的“静中观未发气象”区别究竟何在?文献不足,不敢妄议。
结语
本文通过评述栗谷在《圣学辑要》“涵养”一节所加的按语,对栗谷有关未发的思想做了分析,具体揭示了他对程、朱之教尤其是朱子观点的继承。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处理对栗谷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富于争议的“四七”之辩的内容,尤其是栗谷有关人心道心或气质变化的思想对其未发之说的影响。囿于语言,笔者对韩国学界丰富的栗谷研究成果虽然很感兴趣却也无法吸收。因此,关于栗谷的未发思想,本文所做,应当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仅就笔者现有的考察来看,说栗谷之学是纯粹的朱子学路数,绝无可疑。栗谷作为一个朝鲜儒者,他对朱子学的熟稔程度,令身为中国学人的笔者感到吃惊,发自内心地表示敬佩。当然,笔者在肯定栗谷对程朱之学的认识与奉持的同时,也指出,栗谷对程朱理论的某些内部矛盾及其学说存在的病痛,似乎还缺乏明确的意识与进一步的讨论。总体上,就有关未发的思想来看,栗谷对朱子学,给笔者的印象是,继承有余,而开发不足。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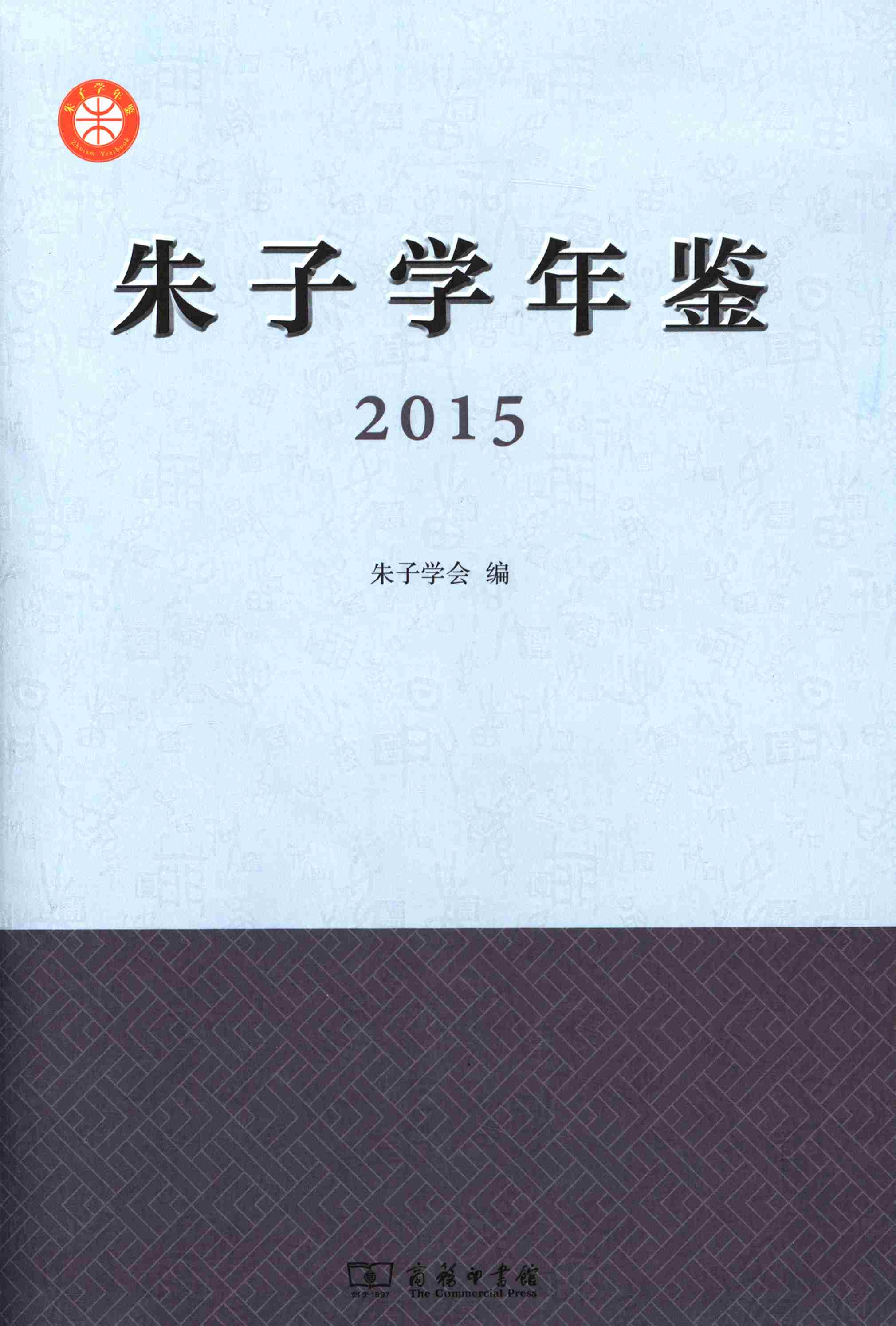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
相关人物
方旭东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