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11 |
| 颗粒名称: | 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8-3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包括阳明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致知与诚意关系的评论、致知是诚意的先行工夫如何可能、引朱子论致知与诚意关系之文献来说明、结论情况。 |
| 关键词: | 朱子学 “诚意” “致知” |
内容
我最近借康德所说的必须对道德从一般的理解进至哲学的理解,才能克服“自然之辩证”,使人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之说,来诠释伊川的从“常知”到“真知”的见解,似乎可以为程朱所以要以穷理、致知格物为工夫,给出一较顺通的说明。而如果程朱所言致知,是对本有的知善恶,即德性之知做进一步的穷究,则由对道德之理之彻底明白,确可起信,而人之私心欲望,自无所容,而不会有借为善而暗中满足私欲的情况出现。而此所谓的“自然之辩证”是人生命中之普遍现象,人必须对治的。若如此解,则致知便有澄清人之意欲,使人不会自欺的功用,如是则致知便可以有诚意的效果,本文拟对此义略做讨论。因对“自然之辩证”义,前已有数文论及,[1]此文从略,而集中在致知乃是对道德义务、道德法则之知及在知道德之理时所会引发的影响上论说。
一、阳明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致知与诚意关系的评论
朱子依《大学》八条目的顺序,认为“诚意”在“格物”“致知”之后,即以“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而他对“致知”的理解是使心知的作用充分发挥,于是“诚意”此一内圣成德的关键工夫是要以对于理有充分的了解为前提,此一诠释固然有《大学》原文做根据,《大学》所说的八条目确是先“致知”才能“诚意”,如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致而后意诚”。故依《大学》,“致知”是“诚意”的根据,意思相当明白。对此一诠释,王阳明做出有力的批评,他说:“纵格得了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了自家意。”[2]阳明认为对于理的认识是知之事,知并不必含行,要在了解了理的意义后,又能依理而行,必须要有另外的工夫,故朱子要提倡敬的工夫,以敬的力量或作用使心依理而行。阳明认为如此理解《大学》并不切于实践,敬的工夫如果如此重要,何以《大学》会把它漏掉呢?[3]故阳明认为“致知”是“致良知”之意,并非推致心知去明理,而是努力推致、实现我们心中本有的良知。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呈现自然有自发的要求朝向天理的方向而实践的力量,依此良知而行就可以有去妄存诚的效果,使我们的现实的生命,成为自发自主地依自己给出的理而实践的道德主体,故若如此解“致知”就可以有“诚意”的结果,工夫在致良知上用,而“致知”就必含“诚意”。阳明之说确是切于实践的,致良知的确当下可以洞开道德行动之源,挺立人的道德主体。牟宗三先生以阳明之说是直贯创生的系统,不同于朱子的横摄系统,分辨十分清楚。牟先生对于朱子由致知而诚意的实践次序的说法也给出了类似于阳明的批评,他认为依朱子所理解的“致知”,并不能达到诚意的结果,若致知是知理的工夫,则从致知到诚意并不能必然相连,故他认为朱子意的诚意,在朱子的理论中是一“软点”[4],即是说朱子意的“诚意”,工夫全在致知上用,而致知是知的工夫,只是知的工夫则不必能开道德行动实践之源。牟先生对朱子意的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及“知之者切,然后贯通得诚意底意思”之言,做了以下的批评:
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黏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求知活动固亦可说是一行动,因而作为行动之源的心意亦可以运用于心知之明之认知而成为真切地去认知,但却并不能限于此而与之为同一。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5]
另外,牟先生认为,依《大学》原文,诚意的工夫有其独立性,虽说八条目的次序是先致知后诚意,但在《大学》的“诚意章”对“诚意”的解释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并没说“所谓诚意在致其知者”,不同于其他纲目的关系的说法。[6]可知依《大学》此处原文,致知与诚意的因果关系亦可打断,诚意的工夫可以独立地做,此即慎独的工夫。
二、致知是诚意的先行工夫如何可能
依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朱子所说的理是当然之理。[7]我觉得从唐先生的说法可以给出对于理之知可以达至诚意的效果之论据。所谓当然之理或道德之理,只是一理所当然或义所当为之“意义”。即是说对于该行之事,吾人只能够因为此事是该行而行,而不能够有别的存心,此即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所谓道德之理就是“为所当为之事只能纯粹的因为当为而为,而不能有其他存心想法。”此一意义,便应是朱子之致知格物穷到底,要了解的“理”。
如果穷理是穷道德之理,而道德之理只是一对义所当为者,只能为了义所当为而为,不能有其他想法,则此理当然是吾人所本知的,因为此义由人的理性而发,没有人会否认此义。举例来说,为子当孝而且其为孝只能因为孝是当为者,不能因为别的目的(如为了贪求父母财产)而孝。此一意义,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且一定赞成而不会反对,如果你反对此义,就表示说,你认为你的儿女可以因为别的目的而孝顺你,而不是因为孝顺是应该的而孝顺。人绝不会同意这种抱着别的目的而行善,为真正的善行。此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一旦知道,便会同意,绝不会否定它。如果否定它,就等于是否定了自己按理而给出来的想法,故反对道德之理,会造成反对自己的理性,甚至自我否定的结果,这是不合理的。故如果理以上述的意思来规定,则对于理的认知,是有对于理本有之知来做根据的,此理并无经验之内容,对此理一反思即得,不假外求,根据此本有之知而进一步地求更清楚的理解便是致知,而如果致知是此义,则越致知便会越明理,此是有保证的。而越明理就会越肯定此理、认同此理,越能认同肯定此理,便会真切希望自己能够表现此理或完全地按照此理而实践。[8]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应该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越了解此理,越知其为当然,则人便会越清楚了解此一意义是绝不能反对的。如此,就可以因着了解的深切,而引发人趋向于要求自己做一个纯粹的为了行所当行而行动的人。如此一来,致知当然会造成诚意的后果,知至与意诚之有因果关系可以成立。
这是从明理、知理而引发人要自诚其意的要求,此知理并非从对理毫无所知来开始,因为此理没有别的,只是义所当为或人应只因为当为而为,不能够做当为之事,另抱有别的目的。道德之理只是此义而无其他,则知之并无困难,甚至对此理之知可以说是先验的,因为对此理的了解虽然要通过认知或思辨的活动,但人稍一反省即可知之,而且所知的理都是一样的,即理是普遍的。如此说则此理并不能是由经验提供的,如果是由经验提供,则人不能都能知此理,而且所知的理也会不一样,而对道德之理的知,伊川正式说为“德性之知”,而且说德性之知不假于见闻。[9]伊川此语很明白表示此理不从经验而得之意。此同于张横渠所言“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之区分。[10]朱子虽然对于此德性之知的说明并不太多,但他认为对于理之知是凡人皆有的,依此意也可以说朱子有对于德性之知是人所本有之意,而且是很清楚的。虽然程朱强调必须要通过格物致知才可以对于理有真知,有真知而后能诚意,而如此才能生起相应于道德法则的行动,但不能因为他们这种说法,就认为他们所言之理与心截然为二,理外于心而为心的对象;或心的知理、心之具理是后天的认知地具。此中的关键在于道德之理的特殊性,此意见后文之讨论。
三、引朱子论致知与诚意关系之文献来说明
牟先生《心体与性体(三)》讨论朱子从致知到诚意的工夫进程,引了朱子相关的重要文献,再做批评。牟先生的批评大意,已见第一节所引。但牟先生所引的朱子原文似乎也可以做另一方向的诠释:
1.“‘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径如此,知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着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处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贵格物,如佛、老之学,它非无长处,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则路径甚明,无有差错,其知所不及处,则皆颠倒错乱,无有是处,缘无格物工夫也。”[11]
朱子所谓的“知得路径”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来规定,故“知至”是从对善恶的“常知”进到“真知”,如果对善恶是本有所知的,则对此从一般的知进至真知,便是对道德上的善恶有透彻的了解,如此,人的私意就不能附着。引文中所说的“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很能表达在人明白了道德义务是理所当然该行之事,吾人实践义务只能为义而行,不能抱有别的目的时,吾人对此便只能完全同意,不能起别的想法。如果不同意,便是反对自己的理性的想法,也等于是自我否定,此所谓“不得不”。如是则朱子所认为的真知“善知当好,恶之当恶”,便“意不得不诚”之论,是合理的,此中从知至到意诚,是可以以因果关系来说明的。
2.问:“物未格时,意亦当诚。”曰:“固然。岂可说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诚!自始至终,意常要诚。如人适楚,当南其辕。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知未至时,虽欲诚意,其道无由。如人夜行,虽知路从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则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临事不如此者,只是实未曾见得。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12]
问者问在物未格时,是否亦要诚意?此问者之意,确如同牟先生所谓的,格物与诚意是可以分开而独立的两种工夫,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打断。朱子对此提问的回应是说,人当然自始至终都要诚意,不能说物未格时,便不用诚意;但若非知至,虽欲诚意,也做不到。朱子此意可表示人本有自发的纯粹地为所当为之要求,故朱子说“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固然未致知时也须诚意,或人亦会有诚其意之要求,但此时的诚意并不真实,如果不真知善恶的不同,便不能真实地诚其意。朱子此处仍旧对“善之当好,恶之当恶”之知有深浅来说,认为人虽然对善恶本有所知,但临事却往往不能为善去恶,此是因为未曾真正见得实理,若对道理能坦然明白,自然会安而行之。如果朱子所要致知穷理的理是道德之理,则如上文所说,真知道德的理,便会有自己对此理完全认同的效果。而朱子此处言理的确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即道德之理来说。则朱子希望由致知达到诚意的效果,也是有理据的。
3.问“‘知至而后意诚’,故天下之理,反求诸身,实有于此。似从外去讨得来”云云。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原注:厉声言“弗思”二字)又笑曰:“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13]
此段问者之意是说知至而有意诚,是格知天下之理,然后反求诸身,使理实有于己。如果是如此,似是从外而求理,即理非吾人本有。朱子回答强调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厉声说此意。当然朱子的“厉声”之反应可能表示问者所说击中了朱子心理为二的理论弱点;但也可以理解为,朱子认为将其理论理解为理在心外,是很不恰当的,即他这格物致知论并不能被了解为理在心外。固然心是活动的,而理是存有而不活动,二者有不同,朱子所说的心,也不是陆王所肯认的心即理的心体;但虽如此,朱子并不认为理在心之外。理固然不同于心,但对于此道德之理——即“善之当好,恶之当恶”,而且为善是因为善之当为而为——是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的,故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在家的儿子与在外的儿子之喻,可以理解为,在心之理与在物之理是一样的,也可以用来区别对此理有常知与真知的不同。
4.问椿:“知极其至,有时意又不诚,是如何?”椿无对。曰:“且去这里子细穷究。”一日禀云:“是知之未极其至。”先生曰:“是则是。今有
二人:一人知得这是善,这是恶;又有一人真知得这是善当为,恶不可为。然后一人心中,如何见得他是真知处?”椿亦无以应。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缓缓寻思,自有超然见到处。”[14]
依朱子意,知至便涵意诚,故他所问的知极其至而意却不诚,当该是知实未能真正极其至,故魏椿所回答的是对的。然后朱子再问,一人知善恶,又一人真知善当为,恶不可为;此二人有何分别?按朱子所要求的答案应该是,真知者见善必为,见恶必去,即真知一定涵实践,另一人虽知善恶,但只是一般地知,不必能贯彻而为行动。而真知所以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是知至一定意诚之故。[15]
5.孝述窃疑:心具众理,心虽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但当其蔽隔之时,心自为心,理自为理,不相赘属。如“二”物未格(牟先生案:“二”当作“一”,下同),便觉此一物之理与“二”不“恨”入(二)当作
“心”,“恨”当作“相”),似为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无之(“邀”当作“邈”)。及既格之,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
未知而无,不以既知而有。然则所以若内若外者,岂其见之异耶?抑亦本无此事,而孝述所见之谬耶?先生批云:极是。[16]
此段李孝述所说的,朱子批云“极是”,应该便可以视作朱子的见解。此段认为理是心本有之物。只是心昏蔽时心与理不相赘属。格物之后,则觉得理是吾人素有之物,依牟先生,此段未能消解理在心外,“似从外去讨得来”之疑问;此处所说的心理的相属或心合理是在格物之后,即心通过后天的认知活动而关联到理。但其实亦可另做解释,此段强调理为心所固有,只是在昏蔽时心理不相属,一旦格之,心便知道理是本来固有的。这里一方面说心与理为二,另一方面说理固具于心,两种意思如何统一呢?我认为未必要如牟先生所说,心理是二,须由认知关联为一;可以用上文所说的由于理是道德之理,而此无条件的为其所当为之意义,是人的理性所首肯而不能反对的,故理虽不同于心,但心一旦明了此理,便会认为此理是吾心本来具有的。从自己对于此理的完全认同,便会觉得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心固然不是道德的本心,但对于道德之理是人心一反省就可以知道之义是屡屡言之的。
在《语类》有一条可以与上说相发明:
德元问:“何谓‘妙众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
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又问:
“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17](僩)
朱子所谓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可以从上文所说的当然之理来说,即人一旦了解此当然之理便会觉得此理是我本有的,非从外得。似乎只有从当然之理来了解朱子所谓的理,才能解消心理为二,但理又为心所本有二说之不一致。朱子于此段文说:“所谓知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即他反对心的知理是知心之外的道理之说,即朱子之意,心与理并不可用主客相对,理是心之外在的对象这一方式来了解。这也可以证上所说的一旦知道当然之理,从理所当然的体会中涵有“此理是我固有的”之肯定。故以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可以解消“心理为二”与“心本具理”二义之相冲突。此段又说,“知”是使本有之理发出来的作用。知不是理,此是当然的,但在知理时,此当然之理的意义,就在我心中显发出来。知此时便成为理的彰显,即由于有此知理之知的作用,让吾人明白了此为吾人所本具之当然之理。而且越知此“本具的当然之理”,越使吾人肯认此理,即认此理为“真实的存在”。
对于理是无条件的当然之理之义,可以从下列诸条见之:
问:“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曰:“只是见得天下事皆我所合当为而为之,非有所因而为之。然所谓天下之事皆我之所当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须是学到那田地,经历磨炼多后,方信得过。”
问为己。曰:“这须要自看,逐日之间,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这便是无所为。且如读书,只道自家合当如此读,合当如此理会身己。才说要人知,便是有所为。如世上人才读书,便安排这个好做时文,此又为人之甚者。”
“‘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无所为,只是见得自家合当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钱谷、笾豆、有司,到当自家理会便理会,不是为别人了
理会。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其亲之病,一则是不忍其亲之死,这都是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器远问:“子房以家世相韩故,从少年结士,欲为韩报仇,这是有所为否?”曰:“他当初只一心欲为国报仇。只见这是个臣子合当做底事,不是为别人,不是要人知。”[18]
《语类》此三段都表明了“为己”,是“无所为而然”之义。为己是无所为而为,而为人便是有所为而为,此“有条件”“无条件”之辨,亦即是义利之辨。能明此义,方可说是知德,而且朱子此三段话都有“见得”之语,表示了对此无所为而然的道理,需要自己看出来。他对无所为而然,规定为“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不是要人道好”“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这些话都显示了朱子对于道德的行为是为了吾人所认为当如此行而行,如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之义,有深切的了解。此可证朱子所说的理当该是道德之理,朱子对于道德行为只是行其所当然之义,有深切的体悟。对于此义,人虽都有了解,“但只恁地强信不得”,要进一步学、磨炼,方信得过。此即是要以格物致知进一步明了此当然的道德之理。
对于道德之理的体认也就是通过义利之辨而得到的理解,此对道德之理的理解不只是理解而已,在理解此理之同时便会生发出朝向此理而力求实践的愿望。于是,从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就会产生实践的力量。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了解到当然之理时,自己一定会肯定此理、赞成此理,而认为此理的规定是吾人本来就该如此做的。此理是我固有之理,既了解此理是我固有的,我所肯认的,那当然我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于是实践的力量就从明理、知理或朱子所说的“知极其至”而生发出来。于是致知的工夫虽然不能造成或达至知与理为一,但在知理的过程中,理的作用在吾人的生命中就得以彰显。道德之理如康德所说是理性的事实,此理性的事实一旦为吾人所了解,就不能不同意。而道德之理的力量就在此处生发出来。此如同上文朱子所说的“用知,方发得出来”之意。
在朱子与陈亮论汉唐的文字中,有以下一段:
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者,盖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莫能夺也,是岂才能血气所能哉![19]
此段说对于天理人欲之分,人不必在古今历史之王霸之迹上探究,只须反省吾心所认为义利、邪正之区分,便可了解。此即表示上文所说对于所谓道德之理,人反省便可知之之意。吾人之心对于义利、邪正之分是清楚的,而对义利之辨“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同于上文所说,对于道德之理之知是使理得到彰显之活动。而“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则也表示了对于道德之理的越加肯认便会越有力量,而自会朝此理的方向实践。此段说明了朱子说统中,知理可以诚意,或在对于理有所知时,理在人的生命中可以发生力量的根据。
四、结论
上文试图说明朱子意的致知格物所以能够达至诚意的论据,此论据的关键在于所知的理是当然之理、道德之理。而吾人对于道德之理一旦有所了解,便会加以肯认、赞同,而感到此理是吾人本有之理,是绝对不能反对的,反对之就等于反对自己的理性,也等于是自我否定。由于道德之理有如此的特性,故明白道德之理就使吾人不得不接受之,而愿意单因为是理的缘故便足以决定吾人的行为,如是就等于是道德之理产生了实践的力量。此道德之理的实践力量,依朱子是通过“知”才能产生的,故理虽然是我本有的,但必须要有知的作用,理的意义才能彰显。而知愈致,理的作用就愈得以生发。我认为如此解应可以为伊川、朱子强调“真知”及朱子意的“知至而后意诚”,做出较为顺当的解释。如果此说可通,则程朱对于道德之理的真知与阳明所说的致良知,都可以是儒家内圣之学的合理的工夫。除了上说之意外,按照康德所说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相涵蕴(互相回溯)之说[20],也可以说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即对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越加了解,越会要求自己的意志需成为自由意志,即明道德之理会给出纯粹化自己的意志的动力。关于此意,我在另外的论文中已有阐述。[21]
当然,众所周知,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范围是很广的,他说一草一木乃至天地万物都有其理,照此说理当该不只是道德的当然之理。但朱子要穷的理虽多,最后是可以通到太极之理的。而太极之理只有一,故理之多,只是虚的多相,所谓“月印万川”。依上文分析,吾人有理由说此作为根源的一理或理之一,是道德的当然之理。又若从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此理可以说是形式之理,只表示了一理所当然,当该无所为地去合做的事之意义,至于在人生的种种的关系、情境中,哪些作为是我们应该无条件的行所当为呢?这就需要加入对于人生种种情境、关系的考虑,而在这个层面上说理,则此理或这些理是有内容的,也需要去格,如对父母的孝顺是应无条件的,因为孝是该行而行的,但怎么样才是具体的孝行呢?则冬温夏凊等恰当的行为也需要研究,这些孝行或礼义便不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意义而已,这也需要去格。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也常指这些意义的理或礼而言,但虽如此,此种种有内容的殊多之理,或礼仪,是在无条件地为所当为之形式之理规定下的,这好比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故此无条件的当然之理,是在先的。故我们还是有理由说,朱子所说的理主要是就此无所为而然的道德之理上说。(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一、阳明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致知与诚意关系的评论
朱子依《大学》八条目的顺序,认为“诚意”在“格物”“致知”之后,即以“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而他对“致知”的理解是使心知的作用充分发挥,于是“诚意”此一内圣成德的关键工夫是要以对于理有充分的了解为前提,此一诠释固然有《大学》原文做根据,《大学》所说的八条目确是先“致知”才能“诚意”,如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致而后意诚”。故依《大学》,“致知”是“诚意”的根据,意思相当明白。对此一诠释,王阳明做出有力的批评,他说:“纵格得了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了自家意。”[2]阳明认为对于理的认识是知之事,知并不必含行,要在了解了理的意义后,又能依理而行,必须要有另外的工夫,故朱子要提倡敬的工夫,以敬的力量或作用使心依理而行。阳明认为如此理解《大学》并不切于实践,敬的工夫如果如此重要,何以《大学》会把它漏掉呢?[3]故阳明认为“致知”是“致良知”之意,并非推致心知去明理,而是努力推致、实现我们心中本有的良知。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呈现自然有自发的要求朝向天理的方向而实践的力量,依此良知而行就可以有去妄存诚的效果,使我们的现实的生命,成为自发自主地依自己给出的理而实践的道德主体,故若如此解“致知”就可以有“诚意”的结果,工夫在致良知上用,而“致知”就必含“诚意”。阳明之说确是切于实践的,致良知的确当下可以洞开道德行动之源,挺立人的道德主体。牟宗三先生以阳明之说是直贯创生的系统,不同于朱子的横摄系统,分辨十分清楚。牟先生对于朱子由致知而诚意的实践次序的说法也给出了类似于阳明的批评,他认为依朱子所理解的“致知”,并不能达到诚意的结果,若致知是知理的工夫,则从致知到诚意并不能必然相连,故他认为朱子意的诚意,在朱子的理论中是一“软点”[4],即是说朱子意的“诚意”,工夫全在致知上用,而致知是知的工夫,只是知的工夫则不必能开道德行动实践之源。牟先生对朱子意的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及“知之者切,然后贯通得诚意底意思”之言,做了以下的批评:
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黏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求知活动固亦可说是一行动,因而作为行动之源的心意亦可以运用于心知之明之认知而成为真切地去认知,但却并不能限于此而与之为同一。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5]
另外,牟先生认为,依《大学》原文,诚意的工夫有其独立性,虽说八条目的次序是先致知后诚意,但在《大学》的“诚意章”对“诚意”的解释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并没说“所谓诚意在致其知者”,不同于其他纲目的关系的说法。[6]可知依《大学》此处原文,致知与诚意的因果关系亦可打断,诚意的工夫可以独立地做,此即慎独的工夫。
二、致知是诚意的先行工夫如何可能
依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朱子所说的理是当然之理。[7]我觉得从唐先生的说法可以给出对于理之知可以达至诚意的效果之论据。所谓当然之理或道德之理,只是一理所当然或义所当为之“意义”。即是说对于该行之事,吾人只能够因为此事是该行而行,而不能够有别的存心,此即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所谓道德之理就是“为所当为之事只能纯粹的因为当为而为,而不能有其他存心想法。”此一意义,便应是朱子之致知格物穷到底,要了解的“理”。
如果穷理是穷道德之理,而道德之理只是一对义所当为者,只能为了义所当为而为,不能有其他想法,则此理当然是吾人所本知的,因为此义由人的理性而发,没有人会否认此义。举例来说,为子当孝而且其为孝只能因为孝是当为者,不能因为别的目的(如为了贪求父母财产)而孝。此一意义,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且一定赞成而不会反对,如果你反对此义,就表示说,你认为你的儿女可以因为别的目的而孝顺你,而不是因为孝顺是应该的而孝顺。人绝不会同意这种抱着别的目的而行善,为真正的善行。此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一旦知道,便会同意,绝不会否定它。如果否定它,就等于是否定了自己按理而给出来的想法,故反对道德之理,会造成反对自己的理性,甚至自我否定的结果,这是不合理的。故如果理以上述的意思来规定,则对于理的认知,是有对于理本有之知来做根据的,此理并无经验之内容,对此理一反思即得,不假外求,根据此本有之知而进一步地求更清楚的理解便是致知,而如果致知是此义,则越致知便会越明理,此是有保证的。而越明理就会越肯定此理、认同此理,越能认同肯定此理,便会真切希望自己能够表现此理或完全地按照此理而实践。[8]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应该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越了解此理,越知其为当然,则人便会越清楚了解此一意义是绝不能反对的。如此,就可以因着了解的深切,而引发人趋向于要求自己做一个纯粹的为了行所当行而行动的人。如此一来,致知当然会造成诚意的后果,知至与意诚之有因果关系可以成立。
这是从明理、知理而引发人要自诚其意的要求,此知理并非从对理毫无所知来开始,因为此理没有别的,只是义所当为或人应只因为当为而为,不能够做当为之事,另抱有别的目的。道德之理只是此义而无其他,则知之并无困难,甚至对此理之知可以说是先验的,因为对此理的了解虽然要通过认知或思辨的活动,但人稍一反省即可知之,而且所知的理都是一样的,即理是普遍的。如此说则此理并不能是由经验提供的,如果是由经验提供,则人不能都能知此理,而且所知的理也会不一样,而对道德之理的知,伊川正式说为“德性之知”,而且说德性之知不假于见闻。[9]伊川此语很明白表示此理不从经验而得之意。此同于张横渠所言“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之区分。[10]朱子虽然对于此德性之知的说明并不太多,但他认为对于理之知是凡人皆有的,依此意也可以说朱子有对于德性之知是人所本有之意,而且是很清楚的。虽然程朱强调必须要通过格物致知才可以对于理有真知,有真知而后能诚意,而如此才能生起相应于道德法则的行动,但不能因为他们这种说法,就认为他们所言之理与心截然为二,理外于心而为心的对象;或心的知理、心之具理是后天的认知地具。此中的关键在于道德之理的特殊性,此意见后文之讨论。
三、引朱子论致知与诚意关系之文献来说明
牟先生《心体与性体(三)》讨论朱子从致知到诚意的工夫进程,引了朱子相关的重要文献,再做批评。牟先生的批评大意,已见第一节所引。但牟先生所引的朱子原文似乎也可以做另一方向的诠释:
1.“‘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径如此,知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着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处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贵格物,如佛、老之学,它非无长处,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则路径甚明,无有差错,其知所不及处,则皆颠倒错乱,无有是处,缘无格物工夫也。”[11]
朱子所谓的“知得路径”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来规定,故“知至”是从对善恶的“常知”进到“真知”,如果对善恶是本有所知的,则对此从一般的知进至真知,便是对道德上的善恶有透彻的了解,如此,人的私意就不能附着。引文中所说的“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很能表达在人明白了道德义务是理所当然该行之事,吾人实践义务只能为义而行,不能抱有别的目的时,吾人对此便只能完全同意,不能起别的想法。如果不同意,便是反对自己的理性的想法,也等于是自我否定,此所谓“不得不”。如是则朱子所认为的真知“善知当好,恶之当恶”,便“意不得不诚”之论,是合理的,此中从知至到意诚,是可以以因果关系来说明的。
2.问:“物未格时,意亦当诚。”曰:“固然。岂可说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诚!自始至终,意常要诚。如人适楚,当南其辕。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知未至时,虽欲诚意,其道无由。如人夜行,虽知路从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则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临事不如此者,只是实未曾见得。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12]
问者问在物未格时,是否亦要诚意?此问者之意,确如同牟先生所谓的,格物与诚意是可以分开而独立的两种工夫,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打断。朱子对此提问的回应是说,人当然自始至终都要诚意,不能说物未格时,便不用诚意;但若非知至,虽欲诚意,也做不到。朱子此意可表示人本有自发的纯粹地为所当为之要求,故朱子说“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固然未致知时也须诚意,或人亦会有诚其意之要求,但此时的诚意并不真实,如果不真知善恶的不同,便不能真实地诚其意。朱子此处仍旧对“善之当好,恶之当恶”之知有深浅来说,认为人虽然对善恶本有所知,但临事却往往不能为善去恶,此是因为未曾真正见得实理,若对道理能坦然明白,自然会安而行之。如果朱子所要致知穷理的理是道德之理,则如上文所说,真知道德的理,便会有自己对此理完全认同的效果。而朱子此处言理的确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即道德之理来说。则朱子希望由致知达到诚意的效果,也是有理据的。
3.问“‘知至而后意诚’,故天下之理,反求诸身,实有于此。似从外去讨得来”云云。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原注:厉声言“弗思”二字)又笑曰:“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13]
此段问者之意是说知至而有意诚,是格知天下之理,然后反求诸身,使理实有于己。如果是如此,似是从外而求理,即理非吾人本有。朱子回答强调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厉声说此意。当然朱子的“厉声”之反应可能表示问者所说击中了朱子心理为二的理论弱点;但也可以理解为,朱子认为将其理论理解为理在心外,是很不恰当的,即他这格物致知论并不能被了解为理在心外。固然心是活动的,而理是存有而不活动,二者有不同,朱子所说的心,也不是陆王所肯认的心即理的心体;但虽如此,朱子并不认为理在心之外。理固然不同于心,但对于此道德之理——即“善之当好,恶之当恶”,而且为善是因为善之当为而为——是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的,故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在家的儿子与在外的儿子之喻,可以理解为,在心之理与在物之理是一样的,也可以用来区别对此理有常知与真知的不同。
4.问椿:“知极其至,有时意又不诚,是如何?”椿无对。曰:“且去这里子细穷究。”一日禀云:“是知之未极其至。”先生曰:“是则是。今有
二人:一人知得这是善,这是恶;又有一人真知得这是善当为,恶不可为。然后一人心中,如何见得他是真知处?”椿亦无以应。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缓缓寻思,自有超然见到处。”[14]
依朱子意,知至便涵意诚,故他所问的知极其至而意却不诚,当该是知实未能真正极其至,故魏椿所回答的是对的。然后朱子再问,一人知善恶,又一人真知善当为,恶不可为;此二人有何分别?按朱子所要求的答案应该是,真知者见善必为,见恶必去,即真知一定涵实践,另一人虽知善恶,但只是一般地知,不必能贯彻而为行动。而真知所以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是知至一定意诚之故。[15]
5.孝述窃疑:心具众理,心虽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但当其蔽隔之时,心自为心,理自为理,不相赘属。如“二”物未格(牟先生案:“二”当作“一”,下同),便觉此一物之理与“二”不“恨”入(二)当作
“心”,“恨”当作“相”),似为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无之(“邀”当作“邈”)。及既格之,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
未知而无,不以既知而有。然则所以若内若外者,岂其见之异耶?抑亦本无此事,而孝述所见之谬耶?先生批云:极是。[16]
此段李孝述所说的,朱子批云“极是”,应该便可以视作朱子的见解。此段认为理是心本有之物。只是心昏蔽时心与理不相赘属。格物之后,则觉得理是吾人素有之物,依牟先生,此段未能消解理在心外,“似从外去讨得来”之疑问;此处所说的心理的相属或心合理是在格物之后,即心通过后天的认知活动而关联到理。但其实亦可另做解释,此段强调理为心所固有,只是在昏蔽时心理不相属,一旦格之,心便知道理是本来固有的。这里一方面说心与理为二,另一方面说理固具于心,两种意思如何统一呢?我认为未必要如牟先生所说,心理是二,须由认知关联为一;可以用上文所说的由于理是道德之理,而此无条件的为其所当为之意义,是人的理性所首肯而不能反对的,故理虽不同于心,但心一旦明了此理,便会认为此理是吾心本来具有的。从自己对于此理的完全认同,便会觉得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心固然不是道德的本心,但对于道德之理是人心一反省就可以知道之义是屡屡言之的。
在《语类》有一条可以与上说相发明:
德元问:“何谓‘妙众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
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又问:
“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17](僩)
朱子所谓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可以从上文所说的当然之理来说,即人一旦了解此当然之理便会觉得此理是我本有的,非从外得。似乎只有从当然之理来了解朱子所谓的理,才能解消心理为二,但理又为心所本有二说之不一致。朱子于此段文说:“所谓知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即他反对心的知理是知心之外的道理之说,即朱子之意,心与理并不可用主客相对,理是心之外在的对象这一方式来了解。这也可以证上所说的一旦知道当然之理,从理所当然的体会中涵有“此理是我固有的”之肯定。故以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可以解消“心理为二”与“心本具理”二义之相冲突。此段又说,“知”是使本有之理发出来的作用。知不是理,此是当然的,但在知理时,此当然之理的意义,就在我心中显发出来。知此时便成为理的彰显,即由于有此知理之知的作用,让吾人明白了此为吾人所本具之当然之理。而且越知此“本具的当然之理”,越使吾人肯认此理,即认此理为“真实的存在”。
对于理是无条件的当然之理之义,可以从下列诸条见之:
问:“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曰:“只是见得天下事皆我所合当为而为之,非有所因而为之。然所谓天下之事皆我之所当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须是学到那田地,经历磨炼多后,方信得过。”
问为己。曰:“这须要自看,逐日之间,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这便是无所为。且如读书,只道自家合当如此读,合当如此理会身己。才说要人知,便是有所为。如世上人才读书,便安排这个好做时文,此又为人之甚者。”
“‘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无所为,只是见得自家合当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钱谷、笾豆、有司,到当自家理会便理会,不是为别人了
理会。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其亲之病,一则是不忍其亲之死,这都是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器远问:“子房以家世相韩故,从少年结士,欲为韩报仇,这是有所为否?”曰:“他当初只一心欲为国报仇。只见这是个臣子合当做底事,不是为别人,不是要人知。”[18]
《语类》此三段都表明了“为己”,是“无所为而然”之义。为己是无所为而为,而为人便是有所为而为,此“有条件”“无条件”之辨,亦即是义利之辨。能明此义,方可说是知德,而且朱子此三段话都有“见得”之语,表示了对此无所为而然的道理,需要自己看出来。他对无所为而然,规定为“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不是要人道好”“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这些话都显示了朱子对于道德的行为是为了吾人所认为当如此行而行,如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之义,有深切的了解。此可证朱子所说的理当该是道德之理,朱子对于道德行为只是行其所当然之义,有深切的体悟。对于此义,人虽都有了解,“但只恁地强信不得”,要进一步学、磨炼,方信得过。此即是要以格物致知进一步明了此当然的道德之理。
对于道德之理的体认也就是通过义利之辨而得到的理解,此对道德之理的理解不只是理解而已,在理解此理之同时便会生发出朝向此理而力求实践的愿望。于是,从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就会产生实践的力量。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了解到当然之理时,自己一定会肯定此理、赞成此理,而认为此理的规定是吾人本来就该如此做的。此理是我固有之理,既了解此理是我固有的,我所肯认的,那当然我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于是实践的力量就从明理、知理或朱子所说的“知极其至”而生发出来。于是致知的工夫虽然不能造成或达至知与理为一,但在知理的过程中,理的作用在吾人的生命中就得以彰显。道德之理如康德所说是理性的事实,此理性的事实一旦为吾人所了解,就不能不同意。而道德之理的力量就在此处生发出来。此如同上文朱子所说的“用知,方发得出来”之意。
在朱子与陈亮论汉唐的文字中,有以下一段:
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者,盖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莫能夺也,是岂才能血气所能哉![19]
此段说对于天理人欲之分,人不必在古今历史之王霸之迹上探究,只须反省吾心所认为义利、邪正之区分,便可了解。此即表示上文所说对于所谓道德之理,人反省便可知之之意。吾人之心对于义利、邪正之分是清楚的,而对义利之辨“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同于上文所说,对于道德之理之知是使理得到彰显之活动。而“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则也表示了对于道德之理的越加肯认便会越有力量,而自会朝此理的方向实践。此段说明了朱子说统中,知理可以诚意,或在对于理有所知时,理在人的生命中可以发生力量的根据。
四、结论
上文试图说明朱子意的致知格物所以能够达至诚意的论据,此论据的关键在于所知的理是当然之理、道德之理。而吾人对于道德之理一旦有所了解,便会加以肯认、赞同,而感到此理是吾人本有之理,是绝对不能反对的,反对之就等于反对自己的理性,也等于是自我否定。由于道德之理有如此的特性,故明白道德之理就使吾人不得不接受之,而愿意单因为是理的缘故便足以决定吾人的行为,如是就等于是道德之理产生了实践的力量。此道德之理的实践力量,依朱子是通过“知”才能产生的,故理虽然是我本有的,但必须要有知的作用,理的意义才能彰显。而知愈致,理的作用就愈得以生发。我认为如此解应可以为伊川、朱子强调“真知”及朱子意的“知至而后意诚”,做出较为顺当的解释。如果此说可通,则程朱对于道德之理的真知与阳明所说的致良知,都可以是儒家内圣之学的合理的工夫。除了上说之意外,按照康德所说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相涵蕴(互相回溯)之说[20],也可以说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即对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越加了解,越会要求自己的意志需成为自由意志,即明道德之理会给出纯粹化自己的意志的动力。关于此意,我在另外的论文中已有阐述。[21]
当然,众所周知,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范围是很广的,他说一草一木乃至天地万物都有其理,照此说理当该不只是道德的当然之理。但朱子要穷的理虽多,最后是可以通到太极之理的。而太极之理只有一,故理之多,只是虚的多相,所谓“月印万川”。依上文分析,吾人有理由说此作为根源的一理或理之一,是道德的当然之理。又若从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此理可以说是形式之理,只表示了一理所当然,当该无所为地去合做的事之意义,至于在人生的种种的关系、情境中,哪些作为是我们应该无条件的行所当为呢?这就需要加入对于人生种种情境、关系的考虑,而在这个层面上说理,则此理或这些理是有内容的,也需要去格,如对父母的孝顺是应无条件的,因为孝是该行而行的,但怎么样才是具体的孝行呢?则冬温夏凊等恰当的行为也需要研究,这些孝行或礼义便不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意义而已,这也需要去格。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也常指这些意义的理或礼而言,但虽如此,此种种有内容的殊多之理,或礼仪,是在无条件地为所当为之形式之理规定下的,这好比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故此无条件的当然之理,是在先的。故我们还是有理由说,朱子所说的理主要是就此无所为而然的道德之理上说。(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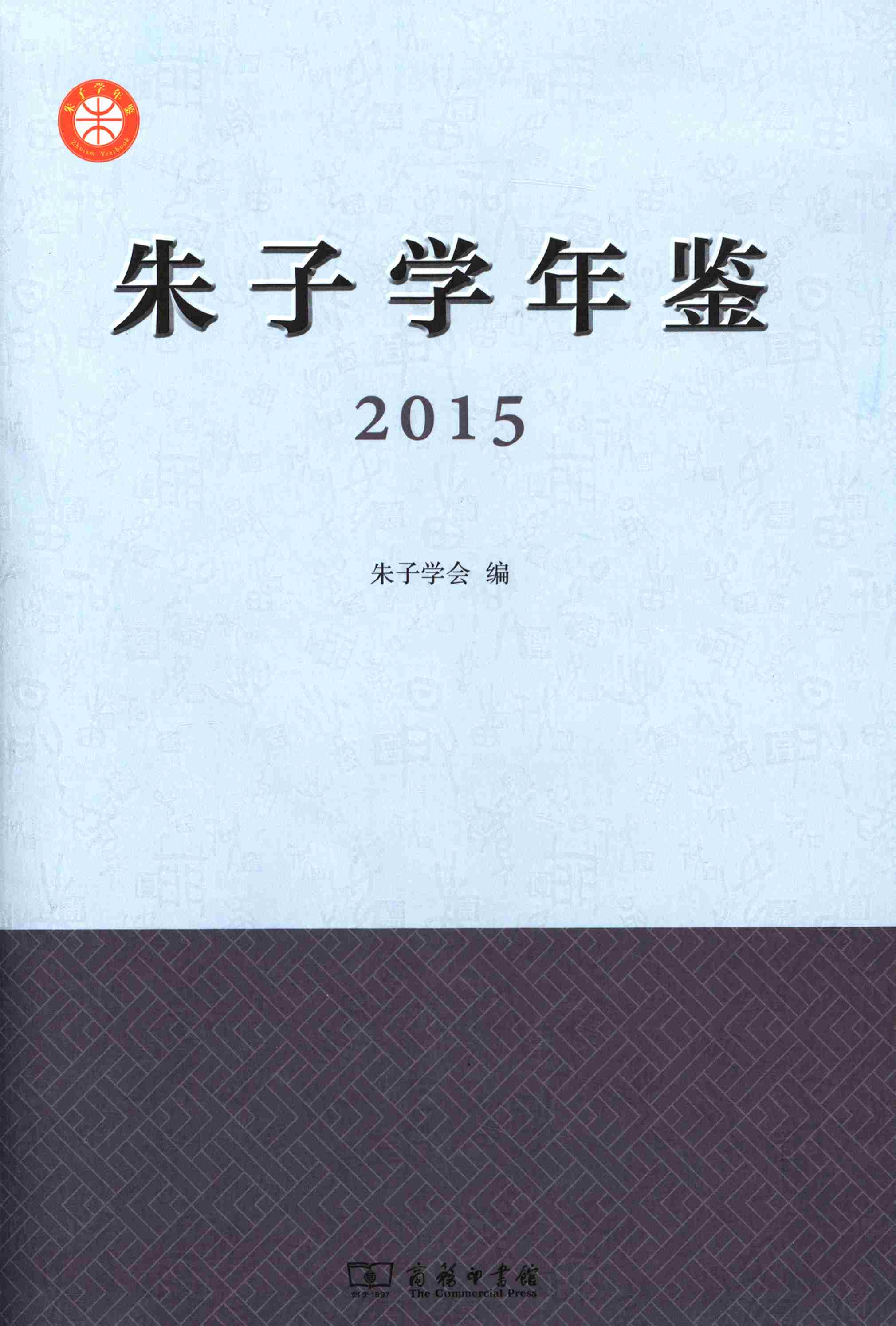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
相关人物
杨祖汉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