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10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8 |
| 页码: | 27-11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包括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等情况。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新视野 |
内容
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
杨祖汉
我最近借康德所说的必须对道德从一般的理解进至哲学的理解,才能克服“自然之辩证”,使人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之说,来诠释伊川的从“常知”到“真知”的见解,似乎可以为程朱所以要以穷理、致知格物为工夫,给出一较顺通的说明。而如果程朱所言致知,是对本有的知善恶,即德性之知做进一步的穷究,则由对道德之理之彻底明白,确可起信,而人之私心欲望,自无所容,而不会有借为善而暗中满足私欲的情况出现。而此所谓的“自然之辩证”是人生命中之普遍现象,人必须对治的。若如此解,则致知便有澄清人之意欲,使人不会自欺的功用,如是则致知便可以有诚意的效果,本文拟对此义略做讨论。因对“自然之辩证”义,前已有数文论及,[1]此文从略,而集中在致知乃是对道德义务、道德法则之知及在知道德之理时所会引发的影响上论说。
一、阳明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致知与诚意关系的评论
朱子依《大学》八条目的顺序,认为“诚意”在“格物”“致知”之后,即以“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而他对“致知”的理解是使心知的作用充分发挥,于是“诚意”此一内圣成德的关键工夫是要以对于理有充分的了解为前提,此一诠释固然有《大学》原文做根据,《大学》所说的八条目确是先“致知”才能“诚意”,如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致而后意诚”。故依《大学》,“致知”是“诚意”的根据,意思相当明白。对此一诠释,王阳明做出有力的批评,他说:“纵格得了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了自家意。”[2]阳明认为对于理的认识是知之事,知并不必含行,要在了解了理的意义后,又能依理而行,必须要有另外的工夫,故朱子要提倡敬的工夫,以敬的力量或作用使心依理而行。阳明认为如此理解《大学》并不切于实践,敬的工夫如果如此重要,何以《大学》会把它漏掉呢?[3]故阳明认为“致知”是“致良知”之意,并非推致心知去明理,而是努力推致、实现我们心中本有的良知。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呈现自然有自发的要求朝向天理的方向而实践的力量,依此良知而行就可以有去妄存诚的效果,使我们的现实的生命,成为自发自主地依自己给出的理而实践的道德主体,故若如此解“致知”就可以有“诚意”的结果,工夫在致良知上用,而“致知”就必含“诚意”。阳明之说确是切于实践的,致良知的确当下可以洞开道德行动之源,挺立人的道德主体。牟宗三先生以阳明之说是直贯创生的系统,不同于朱子的横摄系统,分辨十分清楚。牟先生对于朱子由致知而诚意的实践次序的说法也给出了类似于阳明的批评,他认为依朱子所理解的“致知”,并不能达到诚意的结果,若致知是知理的工夫,则从致知到诚意并不能必然相连,故他认为朱子意的诚意,在朱子的理论中是一“软点”[4],即是说朱子意的“诚意”,工夫全在致知上用,而致知是知的工夫,只是知的工夫则不必能开道德行动实践之源。牟先生对朱子意的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及“知之者切,然后贯通得诚意底意思”之言,做了以下的批评:
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黏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求知活动固亦可说是一行动,因而作为行动之源的心意亦可以运用于心知之明之认知而成为真切地去认知,但却并不能限于此而与之为同一。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5]
另外,牟先生认为,依《大学》原文,诚意的工夫有其独立性,虽说八条目的次序是先致知后诚意,但在《大学》的“诚意章”对“诚意”的解释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并没说“所谓诚意在致其知者”,不同于其他纲目的关系的说法。[6]可知依《大学》此处原文,致知与诚意的因果关系亦可打断,诚意的工夫可以独立地做,此即慎独的工夫。
二、致知是诚意的先行工夫如何可能
依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朱子所说的理是当然之理。[7]我觉得从唐先生的说法可以给出对于理之知可以达至诚意的效果之论据。所谓当然之理或道德之理,只是一理所当然或义所当为之“意义”。即是说对于该行之事,吾人只能够因为此事是该行而行,而不能够有别的存心,此即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所谓道德之理就是“为所当为之事只能纯粹的因为当为而为,而不能有其他存心想法。”此一意义,便应是朱子之致知格物穷到底,要了解的“理”。
如果穷理是穷道德之理,而道德之理只是一对义所当为者,只能为了义所当为而为,不能有其他想法,则此理当然是吾人所本知的,因为此义由人的理性而发,没有人会否认此义。举例来说,为子当孝而且其为孝只能因为孝是当为者,不能因为别的目的(如为了贪求父母财产)而孝。此一意义,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且一定赞成而不会反对,如果你反对此义,就表示说,你认为你的儿女可以因为别的目的而孝顺你,而不是因为孝顺是应该的而孝顺。人绝不会同意这种抱着别的目的而行善,为真正的善行。此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一旦知道,便会同意,绝不会否定它。如果否定它,就等于是否定了自己按理而给出来的想法,故反对道德之理,会造成反对自己的理性,甚至自我否定的结果,这是不合理的。故如果理以上述的意思来规定,则对于理的认知,是有对于理本有之知来做根据的,此理并无经验之内容,对此理一反思即得,不假外求,根据此本有之知而进一步地求更清楚的理解便是致知,而如果致知是此义,则越致知便会越明理,此是有保证的。而越明理就会越肯定此理、认同此理,越能认同肯定此理,便会真切希望自己能够表现此理或完全地按照此理而实践。[8]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应该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越了解此理,越知其为当然,则人便会越清楚了解此一意义是绝不能反对的。如此,就可以因着了解的深切,而引发人趋向于要求自己做一个纯粹的为了行所当行而行动的人。如此一来,致知当然会造成诚意的后果,知至与意诚之有因果关系可以成立。
这是从明理、知理而引发人要自诚其意的要求,此知理并非从对理毫无所知来开始,因为此理没有别的,只是义所当为或人应只因为当为而为,不能够做当为之事,另抱有别的目的。道德之理只是此义而无其他,则知之并无困难,甚至对此理之知可以说是先验的,因为对此理的了解虽然要通过认知或思辨的活动,但人稍一反省即可知之,而且所知的理都是一样的,即理是普遍的。如此说则此理并不能是由经验提供的,如果是由经验提供,则人不能都能知此理,而且所知的理也会不一样,而对道德之理的知,伊川正式说为“德性之知”,而且说德性之知不假于见闻。[9]伊川此语很明白表示此理不从经验而得之意。此同于张横渠所言“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之区分。[10]朱子虽然对于此德性之知的说明并不太多,但他认为对于理之知是凡人皆有的,依此意也可以说朱子有对于德性之知是人所本有之意,而且是很清楚的。虽然程朱强调必须要通过格物致知才可以对于理有真知,有真知而后能诚意,而如此才能生起相应于道德法则的行动,但不能因为他们这种说法,就认为他们所言之理与心截然为二,理外于心而为心的对象;或心的知理、心之具理是后天的认知地具。此中的关键在于道德之理的特殊性,此意见后文之讨论。
三、引朱子论致知与诚意关系之文献来说明
牟先生《心体与性体(三)》讨论朱子从致知到诚意的工夫进程,引了朱子相关的重要文献,再做批评。牟先生的批评大意,已见第一节所引。但牟先生所引的朱子原文似乎也可以做另一方向的诠释:
1.“‘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径如此,知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着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处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贵格物,如佛、老之学,它非无长处,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则路径甚明,无有差错,其知所不及处,则皆颠倒错乱,无有是处,缘无格物工夫也。”[11]
朱子所谓的“知得路径”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来规定,故“知至”是从对善恶的“常知”进到“真知”,如果对善恶是本有所知的,则对此从一般的知进至真知,便是对道德上的善恶有透彻的了解,如此,人的私意就不能附着。引文中所说的“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很能表达在人明白了道德义务是理所当然该行之事,吾人实践义务只能为义而行,不能抱有别的目的时,吾人对此便只能完全同意,不能起别的想法。如果不同意,便是反对自己的理性的想法,也等于是自我否定,此所谓“不得不”。如是则朱子所认为的真知“善知当好,恶之当恶”,便“意不得不诚”之论,是合理的,此中从知至到意诚,是可以以因果关系来说明的。
2.问:“物未格时,意亦当诚。”曰:“固然。岂可说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诚!自始至终,意常要诚。如人适楚,当南其辕。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知未至时,虽欲诚意,其道无由。如人夜行,虽知路从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则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临事不如此者,只是实未曾见得。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12]
问者问在物未格时,是否亦要诚意?此问者之意,确如同牟先生所谓的,格物与诚意是可以分开而独立的两种工夫,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打断。朱子对此提问的回应是说,人当然自始至终都要诚意,不能说物未格时,便不用诚意;但若非知至,虽欲诚意,也做不到。朱子此意可表示人本有自发的纯粹地为所当为之要求,故朱子说“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固然未致知时也须诚意,或人亦会有诚其意之要求,但此时的诚意并不真实,如果不真知善恶的不同,便不能真实地诚其意。朱子此处仍旧对“善之当好,恶之当恶”之知有深浅来说,认为人虽然对善恶本有所知,但临事却往往不能为善去恶,此是因为未曾真正见得实理,若对道理能坦然明白,自然会安而行之。如果朱子所要致知穷理的理是道德之理,则如上文所说,真知道德的理,便会有自己对此理完全认同的效果。而朱子此处言理的确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即道德之理来说。则朱子希望由致知达到诚意的效果,也是有理据的。
3.问“‘知至而后意诚’,故天下之理,反求诸身,实有于此。似从外去讨得来”云云。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原注:厉声言“弗思”二字)又笑曰:“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13]
此段问者之意是说知至而有意诚,是格知天下之理,然后反求诸身,使理实有于己。如果是如此,似是从外而求理,即理非吾人本有。朱子回答强调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厉声说此意。当然朱子的“厉声”之反应可能表示问者所说击中了朱子心理为二的理论弱点;但也可以理解为,朱子认为将其理论理解为理在心外,是很不恰当的,即他这格物致知论并不能被了解为理在心外。固然心是活动的,而理是存有而不活动,二者有不同,朱子所说的心,也不是陆王所肯认的心即理的心体;但虽如此,朱子并不认为理在心之外。理固然不同于心,但对于此道德之理——即“善之当好,恶之当恶”,而且为善是因为善之当为而为——是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的,故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在家的儿子与在外的儿子之喻,可以理解为,在心之理与在物之理是一样的,也可以用来区别对此理有常知与真知的不同。
4.问椿:“知极其至,有时意又不诚,是如何?”椿无对。曰:“且去这里子细穷究。”一日禀云:“是知之未极其至。”先生曰:“是则是。今有
二人:一人知得这是善,这是恶;又有一人真知得这是善当为,恶不可为。然后一人心中,如何见得他是真知处?”椿亦无以应。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缓缓寻思,自有超然见到处。”[14]
依朱子意,知至便涵意诚,故他所问的知极其至而意却不诚,当该是知实未能真正极其至,故魏椿所回答的是对的。然后朱子再问,一人知善恶,又一人真知善当为,恶不可为;此二人有何分别?按朱子所要求的答案应该是,真知者见善必为,见恶必去,即真知一定涵实践,另一人虽知善恶,但只是一般地知,不必能贯彻而为行动。而真知所以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是知至一定意诚之故。[15]
5.孝述窃疑:心具众理,心虽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但当其蔽隔之时,心自为心,理自为理,不相赘属。如“二”物未格(牟先生案:“二”当作“一”,下同),便觉此一物之理与“二”不“恨”入(二)当作
“心”,“恨”当作“相”),似为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无之(“邀”当作“邈”)。及既格之,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
未知而无,不以既知而有。然则所以若内若外者,岂其见之异耶?抑亦本无此事,而孝述所见之谬耶?先生批云:极是。[16]
此段李孝述所说的,朱子批云“极是”,应该便可以视作朱子的见解。此段认为理是心本有之物。只是心昏蔽时心与理不相赘属。格物之后,则觉得理是吾人素有之物,依牟先生,此段未能消解理在心外,“似从外去讨得来”之疑问;此处所说的心理的相属或心合理是在格物之后,即心通过后天的认知活动而关联到理。但其实亦可另做解释,此段强调理为心所固有,只是在昏蔽时心理不相属,一旦格之,心便知道理是本来固有的。这里一方面说心与理为二,另一方面说理固具于心,两种意思如何统一呢?我认为未必要如牟先生所说,心理是二,须由认知关联为一;可以用上文所说的由于理是道德之理,而此无条件的为其所当为之意义,是人的理性所首肯而不能反对的,故理虽不同于心,但心一旦明了此理,便会认为此理是吾心本来具有的。从自己对于此理的完全认同,便会觉得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心固然不是道德的本心,但对于道德之理是人心一反省就可以知道之义是屡屡言之的。
在《语类》有一条可以与上说相发明:
德元问:“何谓‘妙众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
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又问:
“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17](僩)
朱子所谓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可以从上文所说的当然之理来说,即人一旦了解此当然之理便会觉得此理是我本有的,非从外得。似乎只有从当然之理来了解朱子所谓的理,才能解消心理为二,但理又为心所本有二说之不一致。朱子于此段文说:“所谓知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即他反对心的知理是知心之外的道理之说,即朱子之意,心与理并不可用主客相对,理是心之外在的对象这一方式来了解。这也可以证上所说的一旦知道当然之理,从理所当然的体会中涵有“此理是我固有的”之肯定。故以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可以解消“心理为二”与“心本具理”二义之相冲突。此段又说,“知”是使本有之理发出来的作用。知不是理,此是当然的,但在知理时,此当然之理的意义,就在我心中显发出来。知此时便成为理的彰显,即由于有此知理之知的作用,让吾人明白了此为吾人所本具之当然之理。而且越知此“本具的当然之理”,越使吾人肯认此理,即认此理为“真实的存在”。
对于理是无条件的当然之理之义,可以从下列诸条见之:
问:“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曰:“只是见得天下事皆我所合当为而为之,非有所因而为之。然所谓天下之事皆我之所当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须是学到那田地,经历磨炼多后,方信得过。”
问为己。曰:“这须要自看,逐日之间,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这便是无所为。且如读书,只道自家合当如此读,合当如此理会身己。才说要人知,便是有所为。如世上人才读书,便安排这个好做时文,此又为人之甚者。”
“‘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无所为,只是见得自家合当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钱谷、笾豆、有司,到当自家理会便理会,不是为别人了
理会。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其亲之病,一则是不忍其亲之死,这都是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器远问:“子房以家世相韩故,从少年结士,欲为韩报仇,这是有所为否?”曰:“他当初只一心欲为国报仇。只见这是个臣子合当做底事,不是为别人,不是要人知。”[18]
《语类》此三段都表明了“为己”,是“无所为而然”之义。为己是无所为而为,而为人便是有所为而为,此“有条件”“无条件”之辨,亦即是义利之辨。能明此义,方可说是知德,而且朱子此三段话都有“见得”之语,表示了对此无所为而然的道理,需要自己看出来。他对无所为而然,规定为“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不是要人道好”“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这些话都显示了朱子对于道德的行为是为了吾人所认为当如此行而行,如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之义,有深切的了解。此可证朱子所说的理当该是道德之理,朱子对于道德行为只是行其所当然之义,有深切的体悟。对于此义,人虽都有了解,“但只恁地强信不得”,要进一步学、磨炼,方信得过。此即是要以格物致知进一步明了此当然的道德之理。
对于道德之理的体认也就是通过义利之辨而得到的理解,此对道德之理的理解不只是理解而已,在理解此理之同时便会生发出朝向此理而力求实践的愿望。于是,从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就会产生实践的力量。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了解到当然之理时,自己一定会肯定此理、赞成此理,而认为此理的规定是吾人本来就该如此做的。此理是我固有之理,既了解此理是我固有的,我所肯认的,那当然我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于是实践的力量就从明理、知理或朱子所说的“知极其至”而生发出来。于是致知的工夫虽然不能造成或达至知与理为一,但在知理的过程中,理的作用在吾人的生命中就得以彰显。道德之理如康德所说是理性的事实,此理性的事实一旦为吾人所了解,就不能不同意。而道德之理的力量就在此处生发出来。此如同上文朱子所说的“用知,方发得出来”之意。
在朱子与陈亮论汉唐的文字中,有以下一段:
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者,盖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莫能夺也,是岂才能血气所能哉![19]
此段说对于天理人欲之分,人不必在古今历史之王霸之迹上探究,只须反省吾心所认为义利、邪正之区分,便可了解。此即表示上文所说对于所谓道德之理,人反省便可知之之意。吾人之心对于义利、邪正之分是清楚的,而对义利之辨“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同于上文所说,对于道德之理之知是使理得到彰显之活动。而“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则也表示了对于道德之理的越加肯认便会越有力量,而自会朝此理的方向实践。此段说明了朱子说统中,知理可以诚意,或在对于理有所知时,理在人的生命中可以发生力量的根据。
四、结论
上文试图说明朱子意的致知格物所以能够达至诚意的论据,此论据的关键在于所知的理是当然之理、道德之理。而吾人对于道德之理一旦有所了解,便会加以肯认、赞同,而感到此理是吾人本有之理,是绝对不能反对的,反对之就等于反对自己的理性,也等于是自我否定。由于道德之理有如此的特性,故明白道德之理就使吾人不得不接受之,而愿意单因为是理的缘故便足以决定吾人的行为,如是就等于是道德之理产生了实践的力量。此道德之理的实践力量,依朱子是通过“知”才能产生的,故理虽然是我本有的,但必须要有知的作用,理的意义才能彰显。而知愈致,理的作用就愈得以生发。我认为如此解应可以为伊川、朱子强调“真知”及朱子意的“知至而后意诚”,做出较为顺当的解释。如果此说可通,则程朱对于道德之理的真知与阳明所说的致良知,都可以是儒家内圣之学的合理的工夫。除了上说之意外,按照康德所说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相涵蕴(互相回溯)之说[20],也可以说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即对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越加了解,越会要求自己的意志需成为自由意志,即明道德之理会给出纯粹化自己的意志的动力。关于此意,我在另外的论文中已有阐述。[21]
当然,众所周知,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范围是很广的,他说一草一木乃至天地万物都有其理,照此说理当该不只是道德的当然之理。但朱子要穷的理虽多,最后是可以通到太极之理的。而太极之理只有一,故理之多,只是虚的多相,所谓“月印万川”。依上文分析,吾人有理由说此作为根源的一理或理之一,是道德的当然之理。又若从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此理可以说是形式之理,只表示了一理所当然,当该无所为地去合做的事之意义,至于在人生的种种的关系、情境中,哪些作为是我们应该无条件的行所当为呢?这就需要加入对于人生种种情境、关系的考虑,而在这个层面上说理,则此理或这些理是有内容的,也需要去格,如对父母的孝顺是应无条件的,因为孝是该行而行的,但怎么样才是具体的孝行呢?则冬温夏凊等恰当的行为也需要研究,这些孝行或礼义便不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意义而已,这也需要去格。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也常指这些意义的理或礼而言,但虽如此,此种种有内容的殊多之理,或礼仪,是在无条件地为所当为之形式之理规定下的,这好比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故此无条件的当然之理,是在先的。故我们还是有理由说,朱子所说的理主要是就此无所为而然的道德之理上说。(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
杨立华
关于理气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朱子哲学的核心。程颐用“所以”二字建立起形上、形下的严格界限,从而埋下了与理气关系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种子。当然,这些问题是到了朱子那里才真正得到充分展开的。
在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当中,理气动静问题最难索解。虽然此前的研究,对此也提出了一些看起来颇具说服力的说法,但其中仍有难以通贯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梳解。本文将“理生气”与“理气动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期对此问题的理解有所推进。
一、从程颐对张载的批评说起
《近思录》第一卷中有这样一段程子的话:
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将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1]正文后小注曰:“此段为横渠形溃反原之说而发也。”
《程氏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中有两段话,与此章相关:
若谓既返之气复将为方伸之气,必资于此,则殊与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气,以为造化?近取诸身,其开阖往来,见之鼻息,然不必须假吸复入以为呼。气则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至如海水,因阳盛而涸,及阴盛而生,亦不是将已涸之气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也。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天地中如洪炉,何物不销铄了?[2]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物销铄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3]
这几段论述都是在批评张载的虚气循环的气化宇宙论。在张载那里,太虚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这样一来,太虚之气也就成了由万物消散而来的气的某种形态,也就是程颐所说的“既斃之形,既返之气”。在程颐看来,万物一旦消散,也就灭尽无余了,不会回复到“太虚”这一气的原初状态,更不会成为新的创生过程的材料和基础。
程颐对张载的批评,朱子是完全认同的。《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有一则材料,与上引《近思录》中程子的话有直接的关联:
又问:“屈伸往来,只是理自如此。亦犹一阖一辟,阖固为辟之基,而辟亦为阖之基否?”曰:“气虽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气,自非既屈之气。气虽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谓‘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4]1这段话里,朱子充分肯定了程颐不能以“既返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的观点。其中,“物亦自一面生出”,强调的是创生的单向性,而不是像张载所讲的那样的循环。
上引《近思录》“近取诸身,百理皆具”一章下,江永集注中有这样一段解说:
果斋李氏曰:往而屈者,其气已散;来而伸者,其气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穷,若以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则是天地间只有许多气来来去去,造化之理不几于穷乎。释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轮回之说。[5]
这里提到的“果斋李氏”即朱子弟子李方子。李方子这段解说尤为透彻,也充分体现出了朱子对此一问题的看法。如果像张载所讲的那样,既散之气反归为太虚,太虚又聚而为气和万物,那么,宇宙间的气就有了恒定的量。所谓的造化不过是形态的改变,新的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了。
综上所述,程、朱对张载的虚气循环的思想的批评,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其一,虚气循环论等于肯定了气作为材料的永恒存在。而程、朱认为,气作为有具体规定的存在者,是有限的,终究会灭尽无余;其二,既然肯定了气或材料的永恒存在,理就只能是气的形式或结构,因此是附属于气的。这样一来,以理为根源的道德价值也就会失去它的根源性。程、朱当然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气是有成有毁的;其三,如果有永恒的气或材料,那么,天地造化就只是永恒材料在形态上的改变而已,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生生不已的创造。不再是生生不已,而只是永恒变化;其四,以永恒的气或材料为基础的造化,也就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依赖有恒定量的既有材料。这在程子和朱子那里,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二、理生气与理必“有”气既然消散的气
是灭尽无余的,也就意味着气的产生不是源自既有的材料,而完全“凭空”而来的。当然,讲气是凭空而来的,并不是道家意义上的无中生有。道家意义上的无中生有,是强调世界有其开端,万物产生之前,有一个绝对空无的阶段。朱子显然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无始无终的。在这没有开端和终结的世界里,具体的、有限的万物有始有终。具体的、有限的万物的产生,根源于凭空而来的有限的、分化的气。这实际上与郭象万物“自生”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6]与郭象不同的是,朱子认为气的产生根源于理。
在朱子那里,理是天地生生不已的根本。所以,“理生气”是很自然的一种理论的表达。朱子讲“理生气”,有两条材料。其一为《性理大全》中所引:“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此条材料经陈来先生考证,出自朱子弟子杨与立所编《朱子语略》。[7]另一条见于《朱子语类》:
谦之问:“天地之气,当其昏明驳杂之时,则其理亦随而昏明驳杂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气自如此。”又问:“若气如此,理不如此,则是理与气相离矣!”曰:“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
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8]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朱子讲到“气虽理之所生”时,并没有受到学生的质疑。由此可见,在当时日常讨论当中,这一表达并不令人惊异。至少,“理生气”的观念是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
但既然“理生气”的观念确是朱子的主张,且为门下弟子普遍接受,那么,为什么在现存的思想资料当中,“理生气”的明确表述却如此鲜见呢?可见,“理生气”或“气虽理之所生”这样的理论表述,并不是以理作为气的产生的根源的思想之准确表达。《语类》卷一有两条观念一致,但表述上略有区别的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是理后生是气,自“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此性自有仁义。[9]问理与气。曰:“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又问:“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未有人时,此理何在?”曰:“也只在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担,或取得一碗,都是这海水。
但是他为主,我为客;他较长久,我得之不久耳。”[10]
前一段材料中的“有是理后生是气”与后一段材料中的“有是理而后有是气”,表达的是相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朱子涉及理气关系的论述中,“生”和“有”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而朱子之所以很少讲“理生气”,则是因为“有是理便有是气”这样的表达更为准确。“理生气”其实只是“理必有气”的思想的一种较为随意的表达而已。
“理必有气”的观念充分体现在朱子关于仁义阴阳的论述当中。在朱子的哲学当中,仁义属理,本不应分阴阳,但朱子又明确有仁阳义阴的论述:
“仁礼属阳,属健;义智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是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11]
仁阳义阴的观念,绝非朱子一时之论。朱子晚年曾与袁枢就此问题论难往复。仁义虽是理,但有仁之理,便有仁之气,有义之理,便有义之气。仁义虽然属理,但已不像太极之理那样的无分别,而是分了段子的。仁作为理,自身便涵一种发舒伸展的倾向;义作为理,则有一种截断收敛的倾向。理必有其固有的“势”,而“势”就落入气的层面了。
理必有其固有倾向,也就是说,理必有气。天下没有不体现出某种气质性倾向的“孤露”之理。太极之理虽无分别,但既是“诚”之理,就体现出实的倾向来。只虚实的定向,已有了气质层面的趋向了。
既然理有其固有的倾向,这固有的倾向又必然有其气质层面的表现。理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就是气。太极是实有的生生之理。一切根源于太极生生之理的东西,有始必有终。始就是阳,就有动的意思;终就是阴,就有静的意思。动静互涵,阴中涵阳、阳中涵阴而成水、火。所以,天地间最初只有水、火二气: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12]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问:“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13]
由水、火二气,再凝结成天地万物。朱子的宇宙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理“有”动静
理气动静问题根源于周惇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有“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的表述。这一表述就自然引生了太极是否有动静的问题。在程颐以“所以”二字特别强调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之前,这个问题还并不构成真正的理论挑战。但在严格地区别了形上、形下,特别是理、气之后,理的动静问题就成了不能回避的哲学困境。在《太极图说解》中,朱子解释说: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14]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之有动静”这一表述。细读整段解说,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表述上的张力。单看“自其微者而观之,则沖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这样的论述,朱子似乎是在说,理当中有动静之理,而这动静之理是气的动静的根源。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动就有动之理,静就有静之理。由此出发,就难免落入柏拉图式的分有说的困境。朱子哲学既强调一本,不可能在根源处便如此支离。[15]
关于理的动静问题,朱子有很多不同的表述。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表述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但如能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中思想的一致性。《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有几则相关的材料:
问“动静者,所乘之机。”曰:“理搭于气而行。”
问“动静者,所乘之机。”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
周贵卿问“动静者,所乘之机”。曰:“机,是关捩子。踏著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16]
这几条材料讨论的都是《太极图说解》中的“动静者,所乘之机”这句话。其中,人乘马的比喻被广泛征引,用以说明朱子的理气动静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比喻。万物皆禀得太极之理,那么,太极之理是否会随万物的运动而运动呢?太极为形而上者,无形迹可言,因此无所谓动静。既然万物皆禀有太极,也可以说太极寓于动静之中。所以朱子说:“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这里,朱子对“机”的解释值得留意。“机,是关捩子”,指能转动的机械。“踏著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强调的是静以动为基,动以静为基,动静互为条件。因此,在解释《通书》中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时,朱子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17]
实际上,“太极之有动静”,其中的“有”字显然是经过了朱子深思熟虑的。《语类》卷九十四载:
梁文叔云:“太极兼动静而言。”曰:“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18]
这里,朱子特别强调不能说太极兼动静。不仅不能说太极兼动静,甚至也不能说太极贯穿在动静之中。
《语类》卷九十四里有一段对话,对太极贯动静的说法,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问:“动静,是太极动静?是阴阳动静?”曰:“是理动静。”问:“如此,则太极有模样?”曰:“无。”问:“南轩云‘太极之体至静’,如何?”
曰:“不是。”问:“又云‘所谓至静者,贯乎已发未发而言’,如何?”曰:“如此,则却成一不正当尖斜太极!”[19]
从表面上看,张栻的讲法与朱子所说静为太极之体、动为太极之用的思想并无二致。朱子之所以不能接受“至静者,贯乎已发未发”的说法,应该是因为如果至静之太极贯穿于动静之中,那也就等于在动静之外别立一太极,从而将太极与动静分隔开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太极有动静”这个讲法,是朱子关于理气动静问题的究竟说法。实际上,太极“有”动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理必“有”气,是相统一的。既然形而上之理,即使是无内在分别的太极,也有其固有的倾向,如太极就有个实的意思,仁就有个动和生的意思,义就有个静和杀的意思,那么,这种固有的倾向就必然体现出某种气质层面的表现。理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就是气。天下没有不具气质性倾向的理,无“孤露”之理。既然理必有气,气则在动静之中。所以,必然的结论就:理有动静。而这也就是朱子理气动静问题的最终结论。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无思有觉、圣凡体别
——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方旭东
前言
《中庸》首章末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提出了“中”“和”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又与“未发”和“发”连在一起,因此,后来宋代新儒家学者在讨论“中和”问题时,也将“未发”和“已发”作为一对独立的范畴加以分析,更由于朱子的加入,“中和”与“未发已发”问题上升为理学最热门的话头之一。在朱子那里,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未发已发”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它们分别指性与情,一是它们分别指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或阶段。[1]这两种含义分别指向理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关于未发工夫,不仅不同的理学家意见不一,乃至像朱子这样的学者,个人意见前后都有变化,使得这一问题十分复杂,也成为今人理解理学工夫论的一个难点。作为朝鲜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的李珥(栗谷,1536~1584),在阐述其儒学思想之时,亦涉及这一议题。了解栗谷对于未发工夫究竟持何观点,不仅对于把握栗谷思想的特质很有必要[2],对于弄清栗谷之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乃至朝鲜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异同,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本文以《圣学辑要》为中心考察栗谷的未发学说,盖栗谷著作虽丰,但与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则是《圣学辑要》一书。该书由五部分构成:统说第一,修己第二,正家第三,为政第四,圣贤道统第五。其中,修己部分最长,又被分成上、中、下三篇,凡十三章。从篇幅上看,“修己”无疑是《圣学辑要》的重点。栗谷为学是典型的程朱进路,伊川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3],栗谷拳拳服膺,“修己”篇的章节安排即充分体现了这一为学顺序:收敛章第三(敬之始)——穷理章第四——正心章第八(敬之终)。正心章详论涵养省察之意,该章前面说涵养,后面说省察。栗谷所说涵养,主要是指静时工夫,属未发范畴[4];而省察则主要是指动时工夫,属已发范畴。在涵养这个部分,栗谷主要选了程颐和朱熹语录,中间加了一段按语。正心章“涵养”一节的选文与按语,构成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栗谷所选诸家语录(包括按语所引),计有:程子(伊川)4条,朱子6条,真德秀(西山)1条,其学问门径及其对朱子的重视,一览无遗。栗谷所加按语,依其内容,可以分为4条:第1条论未发时无思虑而知觉不昧,第2条论未发时有无见闻,第3条论常人与圣贤未发之中之同异,第4条论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属未发工夫还是已发工夫。不难看出,这些按语都紧紧围绕未发问题展开,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尽在其中,而其关键则是未发时到底有无知觉。
1.未发之时,此心寂然,固无一毫思虑。但寂然之中,知觉不昧,有如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也。此处极难理会,但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据此可知,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包含两个要点:首先,未发时无思(毫无思虑);其次,未发时有觉(知觉不昧)。不难看出,这两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按照平常的理解,知觉与思虑很难分开。对于栗谷之说,很容易提出如下疑问:既然知觉不昧,也就是说,人有清醒的知觉,如何又能做到无一毫思虑?难道思虑不属于知觉?如果思虑不属于知觉,那么,栗谷所说的知觉又是指什么?
一、无思有觉
栗谷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要理解他所说的这两点,存在很大的困难,所谓“此处极难理会”。因此他建议,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敬守此心”即可。如果将栗谷此说与程颐答苏昞(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章做一对照,不难发现二者相似之处:
或曰:“先生(按:程颐)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一作最)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202页)
此节讨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究竟属动还是静,程颐先是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大概他自己也感到这个回答可能让人无可措手,遂告诉对方还是先去理会“敬”。栗谷在处理未发问题时,几乎照搬了伊川的教法。事实上,栗谷在选文中就收了伊川这一条材料。[5]
然而,在解释“敬以涵养”的具体方法(术)时,栗谷又回到未发的两个要点上来:“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看来,不弄清无思(思虑、念虑)有觉(知觉不昧、无少昏昧)的确切含义,也无法去做“敬以涵养”的工夫。
看下面这段话,栗谷所说的知觉似乎主要指见闻这类感觉。
2.或问:“未发时亦有见闻乎?”臣(按:栗谷自称)答曰:“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矣。若物之过乎目者,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过乎耳者,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虽有见闻,不作思惟,则不害其为未发也。故程子曰‘目须见,耳须闻’,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以此观之,未发时亦有见闻矣。”(《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虽然问者没有直接就“未发时是否有知觉?”来请教,但“未发时是否有见闻?”这个问题与未发时思虑知觉的讨论显然相关。问者似乎困惑于“未发时亦有见闻”这样的说法,言下之意:有所见闻不就意味着已发吗?
栗谷了解问者心中之疑,所以一上来就说:在一般情况下,见物闻声往往会随之产生念虑,这当然属于已发状态。但他接着又指出,并不是所有闻见都一定会伴随着念虑,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物过乎目,人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物过乎耳,人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总之,虽有见闻,但人不作思惟。按照栗谷,这种情况应当被承认为未发。换句话说,不是有闻见就一定属于已发。在未发状态下,人一样可以有所闻见。这样,有无闻见这一点不应当被用来区分已发未发,有无思惟才是关键。那么,栗谷所说的“思惟”,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这句话来看,“思惟”是指伴随所见所闻而起念。而从“不起见之之心”“不起闻之之心”这些话来看,“思惟”又似乎是指有目的或计划性的意识活动。如果说前者是起念于闻见之后,那么,后者就是起意于闻见之前。相应的,“不作思惟”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有所闻见,但在头脑(内心)没有激起任何联想、情感、欲求;另一种是没有打算闻见或没有任何闻见的冲动而被动地闻见。[6]
以上是分析的说法,在栗谷本人那里可能没有这样的自觉。对他而言,无论是起念还是着意,都代表着一种自我控制或决定的意向性活动,既不同于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反应,也不同于闻、见这样的主要与身(与心相对)相连的感觉或认知行为,后两种精神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不受自我控制或决定,俗语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有以形容之。
关于自我控制的意向性活动与情感反应和具身性认知活动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说明。通常,只要眼睛是睁着的,只要视力正常,当眼前出现一片樱花,人就会看到,得到感官方面的印象:好漂亮的樱花。这个行为不需要主体意志(will)参与其中,无关于意志或意向。春天看到樱花盛开,觉得赏心悦目,乃至流连忘返,这种情感反应也不是出于主体有意而为。但是,是留在书房里完成论文还是去公园赏花,这些行为则是由主体决断的。栗谷说的思惟,更多是主体决断的意志或意向活动。强调未发时有见闻,无非是想对闻见这类比较简单的感觉或知觉活动与思考、意欲这类相对复杂的理智、情感活动做出区分。就提出已发未发概念的《中庸》本文来说,未发主要是与喜怒哀乐等情感或情绪反应连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庸》并没有说“未发时感觉器官处于沉睡状态”,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作者,本来不会产生未发时有无见闻知觉这样的问题。那么,未发有无见闻知觉,是何时以及怎样变成了一个问题呢?历史地看,这是程颐、朱熹这些宋代理学家努力的结果。[7]事实上,栗谷这段话就提到了程、朱各一条语录。它再次显示,栗谷有关未发的看法是以程朱为旨归的。下面,我们就逐一参详。
2.1目须见,耳须闻。(程颐)
这句话出自伊川答苏季明问后章第11节[8],栗谷在选文中对原文做了具录:
(程子语录3)或曰:“当静坐时,物之过乎前者,还见不见?”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也。若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关于静坐时是否有见闻,伊川给了一个语境主义的回答:“看事如何”,有大事时(比如祭祀)无所见亦无所闻,而无事时则有所见亦有所闻。何以有此不同?伊川没有解释。此节与同章第3节可共看,后者亦是关于未发之前(当中之时)有无见闻的问答,其文如下:
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
如同之前有关动静的回答一样,伊川有关闻见的这个回答,亦有试图照顾两边的特点:一方面肯定目无见耳无闻,另一方面也提示见闻之理仍在。
将第3节与第11节对照,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按第3节,静时(当中之时)无见闻;按第11节,静时(无事时)有见闻。静时到底有无见闻?伊川的说法应以哪一个为准?又或者,伊川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朱子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耳有闻目有见。
如耳无闻目无见之答,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其误必矣。盖未发之时,但为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见,耳之有闻,则当愈益精明而不可乱,岂若心不在焉,而遂废耳目之用哉?(《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可见朱子是以第11节的说法为准,准确地说,是以第11节后半截“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为准。伊川关于“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的说法在朱子看来是错误的。
但其(按伊川)曰“当祭祀时,无所见闻”,则古人之制祭服而设旒黈,虽曰欲其不得广视杂听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为真足以全蔽其聪明,使之一无见闻也。若曰履之有绚,以为行戒;尊之有禁,以为酒戒,然初未尝以是而遂不行不饮也。若使当祭之时,真为旒黈所塞,遂如聋瞽,则是礼容乐节,皆不能知,亦将何以致其诚意,而交于鬼神哉?程子之言,决不如是之过也。(《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按此分析,伊川答苏季明问的这条记录还存在失真问题。[9]总体上,朱子对伊川答苏季明之后章评价甚低:“程子备矣,但其答苏季明之后章,记录多失本真,答问不相对值”[10],“大抵此条最多谬误,盖听他人之问,而从旁窃记,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问者之情,是以致此乱道而误人耳。”(《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61~562页)[1]
朱子之所以坚持未发时亦有见闻,在哲学上,是基于他对两组概念所做的区分:心之知、耳之闻、目之见是一组,心之思、耳之听、目之视是一组。前者属未发,后者属已发。
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虽未发而未尝无;心之有思乃与耳之有听、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一有此则不得未发。故程子以有思为已发则可,而记者以无见无闻为未发则不可。若苦未信,则请更以程子之言证之。如称许渤为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尝有如此圣人?[12]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为非,此言皆何谓邪?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答吕子约第三十九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3页)
朱子对思、听、视的用法与一般无异,都是以之为动词,表示认识活动意。但朱子对知、闻、见的用法与一般则不同,一般是以之为认识的结果或内容,而朱子则以之为认识的能力。通常,人们会说:思而不知(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表示:真正的认识活动必须有意识(consciousness)参与其中,否则,就会出现没有结果的认识活动。朱子为了合于未发已发的规定,故于思、听、视不取活动义,而取能力义。实际上,准确表达朱子意思的词应该是:思考力、听力、视力,而不是:思、听、视。朱子所说的“有知觉”或“知觉不昧”,正是说认识能力或潜能,而不是说认识活动或认识结果。在未发的状态下,当然不能说有知、闻、见,但可以说有思考力、听力、视力。如果朱子只是强调未发状态下,心体的明觉不曾失去,这当然是不错的。就像以镜为喻:镜未照物,不妨其有光明(即能照之功),但不能说其中有影(所照之物影)。但是,当朱子说未发时有见有闻,在语义上就存在歧义,人们会以为是在说有所见有所闻(事实上,朱子本人有时就是这样用的,比如,他在上引这段话里就说“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这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如果没有有意识地去认识(思、听、视),何谈认识的结果或内容(知、闻、见)?而按伊川之见,有思即是已发[13,那么,有所见有所闻又如何还能说是未发呢?
这里的问题出在“思”上。由于伊川并没有规定“思”特指分散心神,使其不专一的“闲思杂虑”,人们当然可以将其广义地理解为所有的知觉活动。事实上,伊川本人有时也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伊川了解,他所说的“思”或“知觉”乃是特指产生使人从所从事的活动当中分散注意力的思虑、念头,再宣称“才思便是已发”或“才知觉便是已发”,就没有问题了。如此看来,未发已发成为问题,纠缠不清,是程朱(尤其是伊川)等人理解的问题,而非《中庸》本文的问题,因为,对《中庸》来说,它明明是讲喜怒哀乐之情的发动与否,而不是对所有知觉活动而言。[14]《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主要是指人心没有生出私心杂念,而并不是说心无知觉。
综观程、朱之说,无论是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还是关于未发时究竟属动还是静,其陈述都存在不能自洽和难以服人之处。栗谷采纳了经过朱子裁断的未发时亦有见闻之说,但从他在选取伊川论未发的语录时依然收入朱子批评甚烈的那条材料这一点来看,伊川之说的内在矛盾以及朱子对伊川的批评与修正,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二、圣凡体别
为驳斥以未有见闻为未发的观点,朱子更发展出一种未发之体上的圣凡区别说,其大意是:未发之时,普通人或有无见无闻之事,而圣人则决不如此,其心聪明洞彻,闻见不爽。栗谷注意到朱子的这个说法,在按语中做了引用。
2.2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朱熹)
此为朱子《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中语,栗谷所引不全,读者从中难知朱子“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之究竟,兹将上下文一并抄录。
须知上四句分别中和,不是说圣人事,只是泛说道理名色地头如此。下面说“致中和”,方是说做功夫处,而唯圣人为能尽之。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若必如此,则《洪范》五事当云“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乃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费尽工夫,却只养得成一枚痴呆罔两汉矣。
(《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35页)
朱子认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这个叙述才是“说做功夫处”,而且“唯圣人为能尽之”。至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只是解释“中”“和”等名词而已。朱子这样理解“致中和”,是把“致”看成动词,这个解释显然受到了《大学》“致知”一词的影响。而把“致中和”功夫看成只有圣人才能完成,则意味着,被子思认为是“天下之大本”的那个“中”,不是常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就能达到的,而只能是圣人才如此。朱子的这个说法在《中庸》本文当中也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如《中庸》第三十一章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第三十二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不过,朱子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却主要是《尚书·洪范》有关“五事”之说。
《尚书·洪范》提到九类常道(九畴),其中第二类就是所谓“五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指:貌、言、视、听、思。《洪范》作者还进一步规定了这五事所应达到的目标:“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汉]孔安国《尚书》卷七“洪范第六周书”,四部丛刊景宋本)从理论上说,恭、从、明、聪、睿这些性质是应然或规范,并不就是实然。不过,古人有一种倾向,即把这些规范看作主体内在自发的美德追求,孔子把这种自发的美德追求称之为“思”,而有所谓“九思”之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第十六》)[15]《礼记·玉藻》也有对君子容貌方面的要求,提出所谓“九容”之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礼记·玉藻第十三》)可以设想,一个君子经过长期修养,他在视听方面自然会达到聪、明之境,而其一举手一投足,也会给人以恭重之感。
从《洪范》本文看,貌、言、视、听、思这五事是各自独立的,但郑玄(127~200)在解释“睿作圣”时,认为“睿”是“通”的意思,还根据孔子说的“圣者,通也,兼四而明”把“圣”解释为“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16],从而,由“思”出发而达到的“圣”就变成了兼包貌、言、视、听四者的更高范畴。易言之,如果一个人通过“思”达到“圣”的境界,那么,他同时也就兼具了貌之恭、言之从、视之明、听之聪。合起来,就是:圣人聪明睿知。“聪明”是就耳目闻见这些感觉或知觉能力而言,本来并不是形容睿智(知)这样的理性能力,现在,经过学者诠释,《洪范》以及《中庸》当中包含了“圣人聪明睿知”这样的命题,就这样,原本形容感觉或知觉能力的聪明与形容理性能力的睿智很自然地结合到一起,并且,它们都统一在“圣”的名义之下。
对于这种聪明睿知的圣人,自然可以说其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其听也聪,其视也明,亦即:即便与事物没有接触,其听之聪、视之明也不会消失。说未发时无见无闻,对于这样的圣人自然不适用。
伊川与苏季明讨论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的问题时,只是一概而论,还没有像朱子这样把常人与圣人分开来说。按照朱子,关于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准确的回答应该是:未发状态下,圣人有见有闻。至此,朱子实际上已对未发状态下“目须见,耳须闻”的说法做了一定的修正,相对于之前他就伊川答苏季明问所做的裁决——未发时,耳有闻目有见,现在这个说法在辞气上已经减弱很多。
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朱子观点的不同版本,都为栗谷所继承。如前所述,栗谷接受了“目须见耳须闻”之说,现在,他也赞成朱子的“圣人未发时有见有闻”论。
3.又问:“常人之心固有未发时矣,其中体亦与圣贤之未发无别耶?”臣(按:栗谷)答曰:“常人无涵养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则乱,中体不立。幸于须臾之顷,不昏不乱,则其未发之中,亦与圣贤无别。但未久而或颓放,或胶扰,旋失其本体,则霎时之中,安能救终日之昏乱以立大本乎?”(《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12页)
在朱子那里,“圣人与常人,其未发之中体是否有别?”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以明晰的方式提出,朱子只是强调,《中庸》所说的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唯有圣人才能如此,至于常人未发之中是如何,朱子则语焉不详。[17]而在栗谷这里,问题已经被尖锐地摆到面前,令他无法回避。栗谷的回答,是“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的一个较强版本。
依栗谷,没有做过涵养省察功夫的常人,其心不昏则乱,因此,其未发之中,与圣人(圣贤)有别。栗谷也提到,常人之心在某些时刻,也许不昏不乱,从而,其未发之中与圣贤无别,但这种时刻稍瞬即逝,总之,都难以担当《中庸》所说的“立天下之大本”的重任。
栗谷关于常人与圣人未发之同异的讨论,其核心涉及如何认识《中庸》所说的“中”。这个“中”,《中庸》既说它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又说它是“天下之大本”。就前一个说法而言,“中”是一个中性描述,只要符合“喜怒哀乐”未萌这个条件,任何人的心,这个时候都可以说是“中”。然而,就后一个说法而言,“中”就变成了价值源泉,从而,再不能说,任何人的心,都可以作为人类的价值源泉。合理的解释,只能像朱子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大本)的,是圣人未发之中。
吕大临(与叔)曾经把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理解为“未发之中”,结果被程颐讥为“不识大本”。伊川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认定赤子之心属已发,而《中庸》所说的“大本”是指“未发之中”。吕大临则为自己辩解说,孟子意义上的赤子之心正是指未发之际而言的,其特点是无所偏倚,完全符合“未发之中”的要求。[18]吕大临在申述时,也谈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同异的问题。
圣人智周万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岂非止取纯一无伪,可与圣人同乎?非谓无毫发之异也。(《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7页)
吕大临承认,赤子与圣人之心有所差异,但他坚持认为,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正是就其与圣人相同而言的。按照吕大临的理解,孟子所说的“纯一无伪”的赤子之心,是指其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易言之,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在其未发时无不同。
朱子在评论程颐答吕大临论中书时,一方面肯定了程颐关于赤子之心不是中而未远乎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对吕大临关于赤子之心属未发的说法也给予了一定的承认。
问:“赤子之心,指已发而言,然亦有未发时。”曰:“亦有未发时,但孟子所论,乃指其已发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无那赤子时
心。”(义刚)(《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问:“赤子之心,莫是发而未远乎中,不可作未发时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发时,也有已发时。今欲将赤子之心专作已发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但其已发未有私欲,故未远乎中耳。”(铢)(《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与伊川一口断定赤子之心指已发的立场相比,朱子的看法显得更为圆融。而关于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之同异,朱子的观点与吕大临也更为接近,因为他说:“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然而,如此一来,朱子关于“常人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之同异”的看法就显出其复杂的一面。
朱子这种“一同”论亦见于另一条材料。
……又问:“‘赤子之心’处,此是一篇大节目。程先生云:‘毫厘有异,得为大本乎?’看吕氏此处不特毫厘差,乃大段差。然毫厘差亦不得。圣
人之心如明镜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论圣人,与叔之失,却是认赤子之已发者皆为未发。”曰:“固是如此,然若论未发时,众人心亦不可与圣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天理别在一处去了。”曰:“如此说,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大抵此书答辞,亦有反为所窘处。当初不若只与论圣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则自分明。”(可学)(《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第2504页)
朱子不同意说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不同,可能主要是基于“性即理”的观念。[19]不过,朱子在对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相同做肯定陈述时,语气并不那么强烈,而是表现出某种审慎:“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如果说众人或常人未发时心多扰扰,那当然不能说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同。按照这个表述,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之心不同的概率要大于相同。栗谷关于圣人与常人未发之体有别还是无别的论述,在思路甚至个别用词上,都与朱子的这个表述有相似之处。有理由相信,栗谷之说是从朱子这里出去。
栗谷论未发的最后一条按语是关于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之说的评论。
4.又问:“延平先生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作何气象,朱子曰‘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此说何如?”臣(按:栗谷)答曰:“才有所
思,便是已发。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故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2页)
“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是朱子评其师李延平之教的话,语出《答何叔京第二书》: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答何叔京第二书》,《文集》卷四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此书写作年月,据陈来考证,当乾道二年丙戌(1166)。[20]时朱子37岁,即丙戌之悟“中和旧说”之际,上距延平之殁(隆兴元年癸未,1163)三载。
栗谷提到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见《语类》卷一百三: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3~2604页)
按:朱子这里所说,只是自悔旧日[21]为李先生撰《行状》时下得语重,并没有点出“以体认字下得重”,盖《行状》原文为“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并无“体认”二字。“以体认字下得重”是栗谷自己的理解。包括前面所说的“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其根据应当都是下面这条语录。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
观时恁著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不观观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4页)
朱子自述,对延平之教以伊川之语格之。这里提到的伊川语,还有栗谷所说的“才有所思,即是已发”,都是出自以下这条语录:
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页)
伊川正确地指出,“求中”之“求”含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计划性在里面,即是“思量”(思),而“既思,即是已发”。所以,“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旦存了求的念头,就不再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状态,而变成已发状态了。对于延平之教,乃至整个龟山门下指诀,朱子的不满,不只是其在名义上说不通,更认为其有所偏。所谓偏,是指这种工夫过于偏向静而忽略了动。朱子认为,伊川的持敬之学相比之下就要中正平和得多。
……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
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596~2597页)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
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却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2页)
问:伊川答苏季明云:“求中于喜怒哀乐,却是已发”。某观延平亦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为如何,此说又似与季明同。曰:但欲见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道,则流于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朱子语类》卷九十六,第2468页)
按照“既思即是已发”的观点,未发时做工夫几乎不可能,因为一有所念,就已经脱离未发状态。程、朱把体验、体认乃至观都理解为思量、思维,不能不说,这种解释太过偏于理性主义,道南一脉,尤其是延平,静中观未发气象,恰恰是以消除目的性或功利性念头(去念,融释)为特征的一种功夫。其日常修炼,以达到内心摆脱一切计较考虑的澄心为效验。
无疑,栗谷是程朱持敬之学的信奉者,以“观(体认、体验)未发时气象”为教法的延平乃至道南一脉的工夫论,与之终不相契,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栗谷对实践未发工夫的延平之教亦保有一份同情,要求“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然而,何谓“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它与延平所说的“静中观未发气象”区别究竟何在?文献不足,不敢妄议。
结语
本文通过评述栗谷在《圣学辑要》“涵养”一节所加的按语,对栗谷有关未发的思想做了分析,具体揭示了他对程、朱之教尤其是朱子观点的继承。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处理对栗谷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富于争议的“四七”之辩的内容,尤其是栗谷有关人心道心或气质变化的思想对其未发之说的影响。囿于语言,笔者对韩国学界丰富的栗谷研究成果虽然很感兴趣却也无法吸收。因此,关于栗谷的未发思想,本文所做,应当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仅就笔者现有的考察来看,说栗谷之学是纯粹的朱子学路数,绝无可疑。栗谷作为一个朝鲜儒者,他对朱子学的熟稔程度,令身为中国学人的笔者感到吃惊,发自内心地表示敬佩。当然,笔者在肯定栗谷对程朱之学的认识与奉持的同时,也指出,栗谷对程朱理论的某些内部矛盾及其学说存在的病痛,似乎还缺乏明确的意识与进一步的讨论。总体上,就有关未发的思想来看,栗谷对朱子学,给笔者的印象是,继承有余,而开发不足。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朱人求
朱子的格物致知既是知识论又是工夫论,是为学的起点,也是为道的起点,是明明德的工夫,“全体大用”思想则是其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然而,何谓“吾心之全体大用”?学术界对此语焉不详。回到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发现,“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就是“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就是仁,就是性体情用,就是心之动静,就是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就是圣人气象等。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影响深远,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以及东亚儒学对此都有不同的诠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心之全体大用”
朱子之学问,如浩瀚的大海,漫无涯际,令人望而生畏。朱子之博大实不可一言以尽之。如果勉强做一概括,我想答案应该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1]。朱子十分明确地表示,“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修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2]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第一义,儒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圣人创作《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所有人都能超凡入圣,一起进入圣人的境域,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格物”二字。四库馆臣也认为,“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3]
格物致知是为学的起点,是为道的起点,也是成圣的起点。何谓“格物”?何谓“致知”?朱子认为,《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于是仿照古人的意思写了一段“格物致知补传”,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的集中阐释,也是其晚年定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4]朱子认为,格就是到,物就是事。穷尽事物的道理,就要认识到极致即无所不到。致就是扩充、推广到极致,知就是识。扩充我的知识,就要做到知无不尽。这就是说,探求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奥秘,不可只停留在表面,要达到它的极处,即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只有持久努力,一旦豁然贯通,则事物的表里精粗、内心的全体大用都能彻底认知,获得一种彻悟性的知识,达到对最高天理的心领神会。这就叫作“物格”,叫作“知至”。“格物”之“物”,并非客观事物,“物犹事也”,尤指人伦物理,其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儒家价值的认同,格物致知乃在于确证内心固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寻找生命存在的社会意义与精神境界,以达到“全体大用”“心与理一”的最高觉悟和最高境界——道的境界、圣人境界。
概言之,朱子的格物致知的最后结果就是悟道,就是“豁然贯通”的悟的境界,具体所指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然而,这样一个彻悟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学术界多语焉不详。
格物致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工夫[5],悟道之后的境界分别对应两种境界,格物的结果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致知的结果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他们的最有利的证据似乎就是朱子回答剡伯问格物、致知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6]实质上,他们只看到第一句,而忽视了第二句。其实朱子格物致知的境界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是“合内外之道”的境界,既有外在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又有内在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二者的统一体。甚至,在朱子看来,“格物所以明此心。”[7]格物只要达到“里”的层面和“精”的层面,就开始达到“心”的全体大用的层面,就达到了“物格而后知至”的效果,“心”的全体大用才是格物的最终归宿。
那么,究竟什么是“表里精粗”呢?朱子认为,表里精粗首先指对“理”的认识的高低深浅。“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只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作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工夫,这唤作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8]“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晓其精,皆不可谓之格。”[9]朱子坚决反对只做表面工夫,不追求终极天理的学人。更反对那些仅仅追求内在真理,又嫌眼前道理粗浅,对事事物物都不理会的学人。理之“表里精粗”是一个整体,表与里、精与粗是天理的一体两面。如果认识达到“知得里,知得精”,二者就达到物格、知至的境地。
其次,表里指“人物之所共由”和“吾心之所独得”。“表者,人物之所共由;里者,吾心之所独得。表者,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
里者,乃是至隐至微,至亲至切,切要处。”[10]如果说,“表”是人物所共行之大道,是外在的,浅表的;那么,“里”就是我内心对大道的独特体认,它是非常隐秘、非常精微的,也是非常亲切可行的,是切中要害的。
再次,表里分别指“博我以文”和“约我以礼”。朱子回答弟子问表里时说:“所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是之谓表。至于‘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是之谓里。”[11]所谓“博我以文”,就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通透无遗,这是从外面的广博而言;所谓“约我以礼”,就是要像自家身心去探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未尽之处,这是从内在的精深处立言。朱子弟子子升感慨地说,自古学问亦不过这两件事情。朱子肯定了子升的观点,更加强调一定要看得通透、彻底,才能到达“知至”的境地。
最后,精粗指认知与境界之高下。朱子在回答弟子问精粗时说:“如管仲之仁,亦谓之仁,此是粗处。至精处,则颜子三月之后或违之。又如‘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充无欲穿窬之心,则义不可胜用’。害人与穿窬固为不仁不义,此是粗底。然其实一念不当,则为不仁不义处。”[12]管仲之“仁”不过是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天下百姓得以保全,故孔子称颂他的仁德,这是指“事”而言,只不过是“仁”的外在表现。[13]而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这是指“心”而言,这才是“仁”的精妙、精微的境界。
在朱子看来,认识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就达到了“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究竟什么是体?什么是全体?究竟什么是用?什么是大用?“安卿问‘全体大用’。曰:‘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此身全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问:‘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如何是体?如何是用?’曰:‘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淳录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体。’”[14]体与用不即不离,体就是用,用就是体。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朱子所称许的“全体大用”呢?
首先,在一般的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5]。”“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6]“明德”即“心之本体”,人心具有万事万物的道理而能自然而然地接应万事万物。但人心受到气质之性的局限,被物欲所遮蔽,有时候不能发出本来固有的光明的德性,“明明德”就是要回到原初那一片光明的德性中去,回归本心原有的澄明。“人之明德,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汩于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云: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则又似必着意体察然后有见。”[17“明德”之“全体大用”具体体现在伦常日用之中,政事的具体运用只是“明德”的向外推衍而已。如果没有觉察到内心的光明的道德,人们就容易沉湎于物欲而不自知,无法恢复本心的自觉与自知。
其次,全体大用一开始指仁体义用。天命之性流行发用于伦常日用和万事万物之中,其全体就是“仁”,万事万物对天命之性的分享和发用,各安其性,各尽其分,这就是义。“熹尝谓天命之性流行,发用见于日用之间,无一息之不然,无一物之不体,其大端全体即所谓仁,而于其间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毫厘之间,不可差谬,即所谓义。立人之道不过二者,而二者则初未尝相离也,是以学者求仁精义,亦未尝不相为用。”[18]仁义是人道的核心价值,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决然分割为二。朱子反对否定精义的空言,认为这是告子“义外”说的错误的根源。如果不知“义”而空谈“仁”,则尽不到仁的全体大用的功用。
再次,在心的运动变化的层面,“全体大用”又指心之动静而言。“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体大用……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岁工夫,屏除旧习,案上只看六经语孟及程氏文字,着开扩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会,方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真实语。”[19]又说:“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此其所以能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也。圆神,方知变化二者阙一则用不妙,用不妙则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20]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动静不失其时,能开物成务,世界一片光明祥和,这就是本心的全体大用。
第四,“全体大用”又指“仁”。朱子认为,“德是逐件上理会底,仁是全体大用,当依靠处。”又说:“据德,是因事发见底;如因事父有孝,由事君有忠。依仁,是本体不可须臾离底。据德,如着衣吃饭;依仁,如鼻之呼吸气。僩”[21]针对蜚卿的提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朱子回答说:“‘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道夫”[22]仁是全体大用,它的发用就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
第五,在推行方式上,全体大用即是推己及人,就是孔子之忠恕之道,即“仁”的具体推衍。“故圣人举此心之全体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达者达人,以己及物,无些私意。如尧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以至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道理都拥出来。人杰”[23]心的向外推衍、发用,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推己及人。尧通过明明德的工夫而达到和睦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天人合一,就是推己及人,就是把儒家忠恕之道发挥到极致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明代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指出:“求终身之行于一言,可谓善学矣!其恕乎!言举斯心推诸彼而已矣!心体与天下相关,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学者苟随所在而扩充之,则全体大用无不由此出矣。非终身可行之道哉?”[24]
第六,在心性结构上,全体大用指性体情用。在心性结构上,朱子主张心、性、情三分,心主性情,心统性情。贺孙因举《大学或问》云:“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元有一贯意思。贺孙”[25]心是心的主宰,心之全体就是仁义礼智之性,心的发用,就是人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性即理,人性之中本来就具有众理,本来就能明万善,只是由于气质和物欲的杂质掺杂其中故昏暗不明。因而,只有剔尽心性的杂质,才能回归心性的光明,回归心性原初的光明的本体。“窃谓人性本具众理,本明万善,由气质物欲之杂,所以昏蔽。上智之资无此杂,故一明尽明,无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杂,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则去得一分之杂,直待所见尽明。所杂尽去,本性方复。学者体此,以致复性之功。”[26]
第七,“全体大用”指“圣人气象”。格物致知即到达圣贤之域。“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纵有敏钝迟速之不同,头势也都自向那边去了。”“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夔孙”[27]格物致知所达到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就是圣贤觉悟之后的境界,每个人一旦优入圣域,圣贤气象油然而生。“夫子之道如天,惟颜子得之夫子许多。大意思尽在颜子身上发见,如天地生物即在物上尽见,天地纯粹之气谓之发者,乃亦足以发之,发不必待颜子言之而后发也。颜子所以发圣人之蕴,恐不可以一事言。盖圣人全体大用,无不一一于颜子身上发见也。”[28]朱子称许的颜子气象就是“圣人气象”,体现出圣人的“全体大用”。这是一种自然和乐、从容、纯粹、澄明的气象,如天地生养万物,自然显现,生机盎然,在万事万物上自然体现。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朱子认为,颜子作为亚圣,其精纯度可得九分,但与孔子的十分和圆熟相比,在境界上还略逊一筹。
二、“心之全体”的具体发用
表面上,朱子格物致知只是追求“心之全体大用”的境界,其实,格物致知所追求的“全体大用”也包含“理”之“全体大用”。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基本遵循的是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即从“德”到“治”的演变。后世许多思想家皆以“全体大用”为朱子理学的精神。[29]朱子充分肯定了弟子描述格物致知贯通之后的“心即理,理即心”的观点:“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先生所谓‘众理之精粗无不到’者,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吾心之光明照察无不周’者,全体大用无不明,随所诣而无不尽之谓……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30]这里的“心即理,理即心”与陆王心学不同,它指心与理不即不离,是格物致知的觉解境界,其实质就是“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意思。朱子强调,理必然有理之功用。“或问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31]朱子甚至声称,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个道理,外王之道与内圣之道也只是一个道理。所谓格物致知,也就是要知晓这个道理而已,这是《大学》一书的基本宗旨。“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颜回同道,岂必在位乃为为政哉!”[32]内圣外王之道,殊途同归,圣王与圣贤同道。大禹、后稷、颜回同道,并不是只有在位才能为政。
《大学》之道,内外一以贯之。“明德”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明德的使命就在于唤醒内在生命的主体自觉,唤醒自己内在光明的德性,排除物欲的遮蔽,回到原初光明澄澈的本心。这个原本光明澄澈的内心包含着万理,自然能应接万物,因而,明明德既是明此心,也是明此理。内心明德的向外推衍,也就是从修身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明此明德,觉此明德,存此明德,不为物欲所遮蔽,只不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更大、任务更重而已。“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所以《大学》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学,则能知觉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学》一书,若理会得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33明明德需要从切近的身心由近及远推至家国天下,明明德的发用就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功效。“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见处理会,也且慢慢自见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识得!……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尧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尧一国之明德;‘黎民于变时雍’,是尧天下之明德。”[34]在朱子看来,明明德不仅要明此心,明此理,还包含着知此理、行此理的意义。“盖所谓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与我一把火,将此火照物,则无不烛。自家若灭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时,又是明其明德。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阙一。若阙一,则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35]光明的本心、透彻的道理就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既照亮了自己的内心,也照亮了他人和整个世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明明德”的工夫,包含着尽知和尽行两个方面。格物、致知就是要知得分明,知到极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要行得分明,行到极处,二者的结合才是朱子的“全体大用”。
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并穷尽事物的道理,它需要在具体事物上落实。格物就是就着具体事物而做穷理的工夫,因此朱子特别强调《大学》以格物的入手工夫就是在于要在事上理会,即事明理,真知力行,否则所认识的道理只是一个悬空的道理。朱子认为:“人多把这道理做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36]朱子格物致知工夫的真正落实,是“知之深”和“行之至”,即真知的获得和实践的圆满完成。致知所获得的“知”是“真知”,既是具有真切的感性经验之知,又是能真切实行的真知。二程指出,“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木。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37]真知就能力行,知而不行,只是认知太浅薄,没有达到致知的目的。在朱子看来,格物致知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夫,它还诉诸行动,致知之“知”是“真知”,即能实行的真正的知识,那些不能真正落实为行动的知识谈不上是“真知”。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只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见识只识到那地位。譬诸穿窬,稍是个人,便不肯做,盖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伤事亦然。”[38]“‘反身而诚’,只是个真知。真实知得,则滔滔行将去,见得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39]只有圣贤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朱子认为,“反身而诚”便是真知。真的知得这个道理,气势磅礴地展开行动,直到见得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地,那种快乐才是无边无际的。朱子以格物致知建立理学,通过格物致知来贯通内在之理与外在之理,内心具备众多的理能自然应接万事万物,使得内外一体,心与理一,全体大用,知行一致。
“全体大用”的精神还必须在实践上予以落实,这也是“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子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有了“全体大用”的精神指引,朱子学在应接万事万物之中有所依仗。这一切不仅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充分体现在朱子书院教化、身心修炼、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理论与实践之中,它们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照亮了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与生活世界。
书院教育的推广。朱子是南宋书院教育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在南宋167所书院中,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有67所,占据40%以上,远远在同时代各位道学大师在之上,其对于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集中体现了朱子书院教化的理念。朱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40]《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作为为学的目标,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它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精神正是传统书院的首要精神。朱子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也就是实施道德教化,即用《尚书》标举的人伦教化于民众。它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道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朱子书院教化尤其重视“知行合一”,注重道德的践履。他接着说:“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41]笃行、修身、处事、接物,无不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笃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项认知的归宿,即把外在的求知转化为内在的生命,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在生命实践中展开落实。这样一来,书院之“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践履人伦则成为“为学”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即做到“穷理”和“笃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白鹿洞书院揭示》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学、问、思、辨,而把浓墨重彩涂抹在“修身”“处事”“接物”等“笃行”事务上,把知识的获得与身心修炼弥合得天衣无缝,这是典型的道学家的教化理念,足见朱子书院教化的经世关怀。[42]《白鹿洞书院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高度凝聚,影响久远,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科玉律。
朱子家礼的实践。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也是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朱子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和福建的民间婚礼基本遵从《朱子家礼》,郑志明先生还在台湾地区推广朱子丧礼,韩国和中国大陆对朱子祭礼都十分重视,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纪念日),韩国和中国大陆都会举行隆重的朱子祭礼仪式。与此关联的是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的勃兴壮大,家谱文化、祠堂文化、宗亲论坛等日益兴盛,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些文化实践活动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它也有力地证明了朱子家礼茂盛的生命力。
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社仓制度,系南宋朱子首创的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孝宗乾道四年(1168),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情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43]淳熙八年(1181),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44]。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它也充分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视民如子、天下一家的淑世情怀。正是通过身心—家—国—天下的一体建构,朱子理学的精神关切也从自我扩充到家族、国家和整个世界。
三、朱子“全体大用”观的发展演变
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对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乃至东亚世界影响深远[4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朱子后学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承传与创新。对于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其晚年得意门生陈淳的理解十分到位并适当发挥。“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圣贤存养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发也,全体卓然,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这里。及其动而应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尔而未尝有丝毫铢两之差,而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亦常自若而未尝与之俱往也。”[46]陈淳指出,心有体有用,“具众理”是体,“应万事”是用,心体寂然不动,这是指性之静而言,感而遂通是其发用,这是指情之动而言。圣贤存养工夫做得好,就能保持内心的贞定,其应接万事自然而然而没有丝毫的差错,这也是程颢、朱子极为推崇的“定性”的工夫和境界。朱子认为,定性就是明明德的工夫:“人心惟定则明。所谓定者,非是定于这里,全不修习,待他自明。惟是定后,却好去学。看来看去,久后自然彻。”[47]只有内心贞定,人心才能一片光明。朱子强调,定性之“定”,并非定在这里,完全不用修养工夫,而心之本体自然光明。[48]定性之后,一定要去学习、修炼,天长日久,自然就能看得透彻。应该肯定,陈淳的理解十分透彻十分系统,对朱子全体大用的四个层次区分得十分明晰。只是陈淳主要在解释“心”的观念,没有办法把“明德”“仁”及其发用、“圣贤气象”等内涵容纳进来。
朱子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的“全体大用”思想基本继承了朱子哲学的精神并有所创发,提出“明体达用”。真德秀认为,全体大用具体表现为“众理”与“万事”的体用关系,故全体大用又可以表达为:“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理即事,事即理”又指理与事(物)之间的体用关系,“体”指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用”指发为实践实行之事。真德秀认为:“大抵理之于事,元非二物。……惟圣贤之学,则以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二者相须,本无二致,此所以为无蔽也。”[49]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在事中,事在理中。真德秀进一步指出,学者求学无非就是穷理以致用,理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用途,功用必定有终极的原理,理就是用,用就是理。“独尝窃谓士之于学,穷理致用而已。理必达于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50]在这里,真德秀批判了佛老(异端)脱离事物空言道理,最后陷入空疏无用;而仅言事实而忽视大道,最终游于无根的粗浅之谈。只有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即用,用即理,二者融会贯通才能称之为学之成。但是怎样才能称为“学之成”呢?真德秀的解答十分精到——“成己成物”,这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为”主要就事功而言。古圣先贤的“为仁”“为邦”分别代表成己成物的极致,它期许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的实现,也即由内圣推至外王,完成王者的事功,建立王者的丰功伟绩,儒学的体用本末都集中体现在这里。
真西山之学,即“明体达用”之学。真德秀极力反对那种把儒家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割裂为二的做法,他说:“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近世顾析而二焉。尚详世变者,指经术为迂;喜谈性命者,诋史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然则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为道之大全乎?故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天理不达诸事,其弊为无用。事不根诸理,其失为亡本。吾未见其可相离也。”[51]真德秀认为,儒家学问有经有史,性命道德之学是经,古今世变之学是史;同时前者又是个“理”,后者则是个“用”。换言之,“成己”是体,“成物”是用;内圣是体,外王是用。善学者应该本经参史、经史互证,这样才能“明理达用”,可见,真德秀努力在内圣和外王之间找到一个调和之处。蒙培元也认为,提倡“经史并用”、要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是真德秀学术的特色,这一点是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52后世多称道他的学说“有体有用”“明体达用”。清代张伯行说:“先生之学卓然有体有用,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也。”[53]清代雷也称:“先生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54]
真德秀还认为《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他运用朱子“全体大用”思想来推衍和阐释《大学》,著成《大学衍义》一书。朱子十分重视《大学》,他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55]又曰:“今且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56]可惜朱子未能完成这一设想,它的完成就是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真德秀指出:“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57]《大学衍义》一书的目的就是让人君明白尧舜禹的体用之学,由内在的修身养性而达之天下,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元代学者对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颇为平淡。元代大儒许谦认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全体即前具众理,大用即前应万事。”“表里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亲其道当孝,此是表;如《孝经》一书之中有许多节目,又诸书言孝节目不一,此是里。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谓其间事为礼节也。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谓事为礼节中之至理也。”[58]许谦对全体大用的理解没有太多的创新,但他对“表里精粗”有所推进,认为,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粗与精的关系于是巧妙地转化为事与理的关系。新安陈栎则基本沿袭了朱子对“全体大用”的理解,他指出,“久字与一旦字相应用力,积累多时,然后一朝脱然通透,吾心之全体即释明德章句所谓具众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谓应万事者也。”[59]元代朱子后学熊禾在他的《考亭书院记》一文中充分肯定朱子之学就是全体大用之学,表现出德与治、本与末的内在关联。“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60]朱子之学还继承了伏羲以来的道统,使得古圣先贤的全体大用之学重新大放光明。
明代邱浚对朱子的全体大用进行了系统的发挥和诠释,尤其重视其中的治道和致用。他认为,全体大用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朱子之学即圣门“全体大用”之学。“朱子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择焉而精,其在章句。语焉而详,其在或问乎。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其朱子自道欤。”“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则为伯道,用非其用,无体故也。学而外此则为异端,体非其体,无用故也。”[61]邱浚指出,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为学者不能离开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来追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离开《大学章句》《或问》来成就帝王之伟业。离开了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治道也就成了有用无体的霸道,治学则是有体无用的异端之学。
其次,《大学》为儒者全体大用之学。“《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62]“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63]在邱浚看来,《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是六经的浓缩精华版,不愧为儒家的全体大用之学的经典文本。邱浚尤其关注《大学》治国、平天下之方略,其《大学衍义补》集中衍义了《大学》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
第三,《易》者其体,《书》者其用。“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64]《易》乃群经之首,义理之宗,学者学习六经成为儒者,讲明义理并以此修身,这就是“全体”之学。其“大用”则表现为治人与为政,它也是学的完成。《书》经是古圣先贤为政的文献,最能体现政治的精神。
第四,“横渠四句”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表达。“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65圣人全体大用之学关乎道统的承传。“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66]从伏羲、尧、舜、禹、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这些圣人都在为有形而无心之天地立心,为有命而不能自遂之生民立命,使得凡夫俗子皆有机会优入圣域。而曾子的《大学》之教,则是为了承接孔子之精神和往圣之精神,接续道统,为万世开太平,承传圣人全体大用之学。横渠的“四句教”则是对《大学》全体大用思想的精练表达,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体现。
最后,全体大用又指“圣德之全体大用”。“臣按:朱熹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67]“圣德之全体大用”指向的是内心至圣之德,它来源于上天“至诚之道”,唯有聪明圣知的圣人才能上达天德,才能完成“全体大用”的功效,实现“全体大用的境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尧舜这样的圣王,邱浚勉励帝王要有所作为,要向三代学习,向尧舜学习,上达天德,成为一代圣君。
四、几点思考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全体”就是心中包含所有的道理,所谓“大用”就是人心自然能应接万事万物。“全体大用”精神落实在实际的社会政治层面,就是朱子书院教化的实践、朱子社仓的建立以及《朱子家礼》的推广,而作为学术层面展开则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礼制研究,足见朱子思想中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致知与力行的统一。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承传与创新,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走向东亚世界,成为东亚思想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仔细梳理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
(一)隐藏在“全体大用”话语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
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68](Barbara Johnstone,第102页)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全体大用”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透过朱子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朱子对内圣精神的推崇,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微言大义”的传统。具体而言,“全体大用”除了朱子《大学章句》所标榜的“明德”和“心具众理而应万事”,还有仁体义用、性体情用、心之动静、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圣人气象等不同的含义,这些内涵在“全体大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结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它们隐藏在结论的背后,被历史所遮蔽。从“仁体义用”到“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朱子哲学所经历的从片面到不断完善的艰辛历程。“全体大用”思想在朱子哲学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揭示,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朱子哲学的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只是朱子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只是其格物致知理论的一个环节。朱子的“格物”只是“明此心”,“全体大用”只是“心”之“全体大用”。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必须回到朱子哲学的心性语境中来定位。“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属于修身的功夫,它的向外发用可以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外在的功用只是心的作用的外推和放大,尽管朱子有诸多的社会关切,但在本质上它仍然属于心性儒学。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社会功用也不宜过分放大,朱子的活动更多还是在书院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其社会事功总体来说建树不大,其在漳州任内正经界和晚年出任帝王师等活动则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也与他的内在于心性的“全体大用”思想紧密相关。
(二)“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
话语具有建构知识和社会的能力。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和沃戴克(R.Wodak)把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概括为: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权力关系是“话语的”(discursive),即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变化的场所;话语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69]后世对朱子的理解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全体大用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它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在陈淳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仍然是一种真理权威,一种知识权力,只是在帮助他们完成心性知识的建构。师生知识共同体,朱子的思想与弟子的思想内部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真德秀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开始获得社会权力,走向权力的中心。元代朱子后学又走向了心性儒学的回归,明代邱浚则在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引导全体大用走向帝王之学。可见,后世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经历了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的互动。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后世对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和演化也基本演绎着德与治、内圣与外王的思想进路。
(三)从“全体大用”的视角重新审视朱子的心与理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后世对其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朱子思想体系的理解。“全体大用”是格物的最后境界和归宿,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最高天理的认识。天理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心”与“理”是“一”还是“二”,二者的分野构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界线。牟宗三先生认为,“心具众理”是认知地具,及“既格”而现实地具之,此理固内在于心矣,然此“内在”是认知地摄之之内在,仍非孟子“仁义内在”之本体地固具之之内在。此种“内在”并不足以抵御“理外”之疑难。此仍是心理为二也。二即是外。[70](牟宗三,第368页)朱子思想的主旨为理学,理是根源性存在,是最高的实体。但并不表示此理只是心外之理,心与理截然为二。朱子虽然承认一物有一物之理,但他的格物就是“明此心”,“明此理”,是“明明德”的工夫。格物致知所到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心”不仅“具众理”,而且“包万理”,还能知“万理”。尽管朱子从本体论上坚决反对“心即理”,但“理”在心中,心具众理。心知众理,心管众理。所谓“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朱子语类》卷十八)一句话,在朱子的思想世界里,理为体,心为用,心包万理,心管万理,全体大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朱子指出,“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朱子语类》卷五)这种“心与理一”的境界,指心与理交相辉映,融为一体,随事而发,物来顺应,自然而然。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心学与理学对“心与理”的区分十分清晰,但在认识论和境界论意义上,“心与理一”是心学与理学家共同信守的基本理念和终极关怀。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哲学系)
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1]
——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
许家星
当朱子于“伪学”声中去世时,朱子学即身陷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在此情况下,以勉斋为首的朱门弟子以竭力弘扬朱子学为己任。在如何诠释朱子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弟子们虽因气质、学问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差异,但总体表现为以发明、维护朱子思想为宗旨。勉斋对朱子四书学的阐发,形成了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元诠释路向,奠定了诠释朱子四书学的基本样式,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勉斋学派,对“后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
勉斋认为,朱子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集注》,但该书精密简严,且与《精义》《或问》《文集》《语类》颇多分歧之处,必须对之展开再阐释,方能把握其旨意所在。《论语通释》即是勉斋对朱子《论语》的诠释之作。据《勉斋年谱》可知,该书为勉斋一生心血所在,成于其生命之终。勉斋以《通释》命名此书,是希望消除朱子论说之分歧,以定于一是。门人对此书给予了高度推崇,认为已将朱子《论语》疏通无遗。陈宓《题叙通释》说:“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2]《通释》对《集注》本旨的发明,主要采用以下方式:揭示《集注》用语、用意、针砭,辨析两说异同,以达到羽翼朱子的目的。
(一)用语、用意、学弊。《集注》用语“浑然如经”,须对之加以拆解式讲解,方能使其意义显明,利于理解。勉斋对《论语》学而章注的“善”和“复初”曾做了如下阐发:“‘明善’谓明天下之理,‘复其初’则复其本然之善也。”[3]很多情况下勉斋直接就《集注》“字义”逐字做出解释,如逐一解释温良恭俭让章“过化存神”四字。
如果说“用语”的解释是说明朱子说了什么,那么“用意”则要进一步揭示“用语”后面的用心所在。勉斋常以“何也”“故曰”等作为引语表示此意,仍以“学而”章注文阐发为例:“言君子而复归于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何也?学而至于成德,又岂有他道哉。”[4]
勉斋尤为留意存在多种诠释可能的文字,如《集注》解“伯夷叔齐”章“怨是用希”为“人亦不甚怨之也”。勉斋认为“怨”的施事主体可以是己、亦可是人,指出《集注》“人怨”解依据的是伯夷叔齐的圣贤境界。
《集注》特别重视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勉斋亦秉承此点。如《集注》为了激发学者修道进德之心,对接舆、沮、溺、丈人给予了高度肯定。勉斋以激昂之辞对四子做了高度赞扬,表达了对贪慕荣利之徒的痛恨。在“吾岂匏瓜”章亦指出,匏瓜是蠢然无知觉之物,人是万物之灵,应有所贡献于世界。世人借夫子此说为谋食四方辩护,丧失进退之义,背离了圣人本旨,必须加以辨正。“世之奔走以糊其口于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圣人之旨矣。”[5]
(二)两说异同。朱子四书学是以《集注》为核心的学术系统,但《集注》与《或问》《语类》等存在差异;《集注》所引二程学派之说与朱子思想存在差异;《集注》前后两解并存之异同值得留意;《集注》历经修改形成的前后差异之说,究竟何者为朱子定见,关乎朱子思想之把握。勉斋针对此四方面异同加以再诠释。
勉斋尤重视《集注》与《或问》的异同,《论孟集注》与《论孟或问》因写作时间、修改历程有别,彼此颇多差异。[6]勉斋对此多采取“两存之可也”的态度。如他指出见危致命章“《集注》以为‘庶乎其可’,则固恶其言之太快,然《或问》之意,则又与《集注》不同。读者两存之可也。”[7]《集注》认为“其可已矣”意在贬子张断语过于伤快,不够周全,但《或问》在比较“可也”与“其可已矣”时则认为前者贬抑,后者揄扬,《或问》说对学者仍有其价值,故当“两存之”。对《集注》与《语类》的不同,勉斋亦主张并存之。《集注》“三月不违”章注引“内外宾主之辨”说,《语类》对此有不同表述,勉斋从文义与义理双重角度给出两说并存的合理性。宾主说大概以屋子为喻,内主外宾,具体有两解:一是以仁为屋,心之出入往来为宾主。“其心三月不违仁”指心是否安于仁,更合乎文本义。二是以身为屋,仁之存亡为宾主,从文义言有所隔阂,但就义理言,此说心仁合一,心即是仁,心在即仁在,于为学工夫更紧切。
勉斋亦注意《或问》文义之误可能产生的义理偏差。如指出《或问》“切磋琢磨”的理解存在不当:
若谓“无谄无骄”为“如切如琢”,“乐与好礼”为“如磋如磨”,则下文“告往知来”一句便说不得。“切磋、琢磨”两句说得来也无精采……前之问答,盖言德之浅深;今之引《诗》,乃言学之疏密。[8]
《集注》指出切磋、琢磨是处理骨角、玉石的由粗到精的两项工序,切琢为粗,磋磨为精。勉斋认为,若将此粗精说直接对应于“无谄无骄”和“乐与好礼”,则会导致下文“告往知来”毫无着落,没有体现子贡的领悟与夫子的赞许,“切磋琢磨”说亦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和力量。此虽为微小文义差别,却不可放过。子贡师徒问答当与《诗》句讨论分开来看,分别指道德境界深浅和学问工夫疏密。
勉斋指出,《集注》引文与朱子注语总体应相互融洽、互为补足,“各有所发明也。”如“可与共学”章程、朱经权之说不同,勉斋认为,《集注》经权有别说使经、权意义分明而不至于混为一团;程子权变本质只是经说亦有道理,朱子所言对程子说具有补足、完善意义,“足以继此章之旨”。面对程、朱之异,包括勉斋在内的门人通常认为朱子解更好。如“祭如在”章,《集注》先引程子以孝敬释祭祀祖先神灵说,再补充己说。勉斋认为,祭祀根本在于真实无妄之诚意,朱子所补“诚意”恰补充了程子说之不足。勉斋有时直接指出程子说“不若《集注》之说为当”。如子夏之门人章的“先后”诠释,程子从教学次第立论,朱子就义理精粗而论,故朱子学更确。勉斋对朱子超越前人的推崇在关于仁的论述中表现得最鲜明,认为“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他在“仁而不佞”章说: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义,则仁之道无余蕴矣。……又断之曰“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深味“全体不息”四字,则学者而求至于仁,其至之标的,又昭然而可见矣。……其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大矣![9]
朱子孝悌为仁之本章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阐发仁的名义,透彻周全,可谓穷其底蕴而无余,本章则以“全体不息”四字昭然标示求仁之方。此四字极其精密含蓄地阐发了仁道及行仁之方,远迈前贤而有功于学者。且“全体”二字已囊括《集注》后章所引延平“当理无私心”之说,“不息”又进一步揭示其言外之意。
勉斋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对程、朱异同并非一味是朱非程,而是以自身判断为准,对朱子说同样有不少批评,有时亦认为“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如关于学而章解,他在《复叶味道书》中说:
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则是君子然后不愠。以悦、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
程子之说,方为稳当。[10]
《集注》所引程子说认为只有做到不愠方才是君子,朱子本人则认为只有成德君子方能做到不愠。据本章悦、乐、不愠三句文本的内在语义关系,程子说更恰当。其实,朱子说和程子说显然互补,勉斋从中看出朱子之不妥,颇出乎意外。
朱子就《集注》前后两说并存的情况有明确解释,认为这是因两说皆有可取,无法舍弃,但前说要优于后说。勉斋据贴切文义和为学工夫的原则对之有所辨析。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忍”,《集注》有忍心、容忍前后两义,但所选范氏说为容忍义、谢氏说为忍心义,这样就使得本应在后的范氏容忍义反而在前。勉斋的解答是:范氏、谢氏论域不同,前者就全章而发,后者仅针对“是可忍”而论。又如人而不仁章《集注》先后引游酢、程子说。游氏以人心解仁,较程子以正理解仁更亲切。朱子同时选用二说,表明仁应当包含人心与正理的统一。在勉斋看来,心与仁的关系更为紧密。
《集注》初本与改本是朱子后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出朱子思想的演变,对准确把握朱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亦能考验学者对朱子思想的把握能力。勉斋指出“博学笃志”章存在初本和改本之别:前者“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过于分析,带有有所为而外求的弊病,后者“所存自熟”则纯从心之存主立论,专注于内心的操存涵养,进一步突出了心与仁的内在一体性,显示出《集注》修改之精密。
《集注》初本谓“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后乃以“所存自熟”易之。
盖初本以博笃切近为“心不外驰”,学志问思为“事皆有益”。其后易之者,则专主于“心之所存”而言也。……以此见《集注》愈改而愈精也。[11]
二、“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勉斋于朱子兼具女婿与弟子双重身份,深知朱子四书诠释用心之勤,故再三告诫学者对《集注》切不可抱轻易之心。出乎意料的是,勉斋在《论语》诠释中,对《集注》却不大客气地给予批评。《复叶味道书》集中表达了他对《集注》的修正看法:
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朱先生云:“敏于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此用《中庸》“有余不敢尽”之语,然所谓“慎”者,非以其有余而慎之也。“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事难行故当勉,言易肆故当慎耳。人而无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当用“其何以观”例。“志道、据德、依仁”不当作次第说,若作次第说,则“游艺”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据德、据德者未能依仁之病。……德则行道而有得于身,随其所得,守之而不失。[12
勉斋指出,不应为了保持统一而删除《语录》不同之说。朱子对二程语录的处理,亦是尽量保持原貌。天下义理无穷,并不能保证编者所见为的当之论。即便朱子穷毕生精力所注之《论语》,亦多有不满人意处,这恰可以借《语录》之说看出,《语录》异说具有参考、矫正《集注》的价值。他举出《集注》中四处错误,从文义、义理、工夫上加以批评:学而章朱子解不如程子说精当;以《中庸》“有余不敢尽”解释“慎于言”不妥,慎只是谨慎勉励,并无有余义;“何以行之”的“以”解为“能够”不对,当解为“居上不宽”章的“凭借”义;志道章《集注》《语录》皆反复言及四者先后次序不可乱、本末精粗必有序,这一视四者为造道次第的观点,不仅导致“游于艺”无所安置,且割裂了志道、据德、依仁与人的关联,学者对道、德、仁皆需要始终用力而不可有须臾放弃,四者在价值序列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它们是并列而非次第关系。在文义上,勉斋还质疑《集注》博文约礼章的“约,要也”说,认为此处约之于礼的“约”显然为动词,是“约之”义,训为“要”不合文理。如训为“约束”,虽合乎文义,却未能突出与“博”的对举义,当合二者而取之,为“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其实质不过是存心而已。勉斋有时会通过否定《集注》所引说来间接表达批评。如“君子九思”章《集注》引程子“九思各专其一”说,勉斋认为专一而思的弊病是泛泛而思却毫无统绪、效果,思应当建立在戒慎敬义的基础上。
历来对十五志学章的理解,存在一个困惑:夫子所言自十五有志至于七十不逾矩的修道历程当如何观之?是开示真实语还是示教象征语?《集注》引程子说,认为“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朱子自评为,“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认为夫子生知之圣,其进道修得次序未必循此阶梯而进,未必有如此明确的渐进过程。但圣人并不自以为是,其说乃为学者展示为学上升之次第,是夫子修道进程的大略标示,希望学者据此为准则而加以对照自勉,并非是夫子内心自以为已达到了圣人境界而托之以此谦虚推脱之辞。故此说虽为夫子的一种谦辞,但此谦辞仍有其真实内容所在。勉斋对此提出了批判性看法:
圣人生知安行,有见夫义理之在人,不啻如饥食渴饮之急,则夫知而必学,学而必好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十年十五年而后一进,亦圣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说者以为圣人立法谦辞以勉人,则圣人皆是架空虚诞之辞,岂圣人正大之心哉!故《集注》虽以勉人为辞而又以独觉其进为说,亦可见矣。[13]
所谓圣人生知安行乃是指知义理之深,学义理之笃,好义理之切,是对学的知之、好之、乐之,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所在。圣人与常人的区别不是从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成就论,而是就其对义理之学的学习态度、能力论。至于十年、十五年的进学层次,则是圣人之学达到某一层次自信的表现,是见之真、行之切的真实自得的流露,并非是圣人为了勉励学者、为学者立法的谦辞。《集注》尽管主张这是圣人之勉辞,但同时又提出是圣人“独觉其进”处。其实,《集注》更强调勉人、立法、谦虚之说,“独觉其进”说不过略有此意而已。勉斋则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以此作为对《集注》的批评修正。
朱子《集注》之修改完善,是在与弟子讲学辩难中展开的。朱子善于包容、吸取意见的学风培育了弟子勇于质疑的学术品格。勉斋尤其保持了这种学风,故对《集注》时加质疑,体现出唯理是从的精神,勇于批判亦成为勉斋学派的一大特色。如传勉斋学的江西一派,以“多不同于朱子”的饶双峰为代表,其对朱子四书义理有着精细辩难,涉及格物传、忠恕解、心性论等核心论题,如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说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指出以朱子之高明、精密,对程子说的理解仍然存在重要差失,可见质疑问难之必要。“《集注》主一而废一,所以于曾子用工处,又别说从一路去。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14]勉斋所传于浙江的北山学派亦秉承此种怀疑批判精神,如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从考据学入手,对《集注》文字音韵训诂等颇多补正。
三、“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
勉斋据当时学术情况,有意彰显了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较之讲学穷理,“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才是工夫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论的内转。
“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勉斋体现出重“心”的立场,视心为万化根本,人身主宰,具有参赞天地之化育,修齐治平之效用,批评世人对心有所轻视。“心者,天地之蕴,化育之机……甚矣,人之轻视其心也。”[15]他于礼云章、人而不仁章辨别《集注》二说优劣时,皆强调心对于理的优先性,事理必须安顿在人心上才有意义,若无心为据依之地,则理是寡头无根的。并于《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中提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的心性为一论,发朱子所未发。说:“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仁义礼智皆具于心,而谓‘心在性外’,可乎?至于为说,则曰‘心出于性’,何其与孟子之言相戾乎?……则此心之妙,但有虚明而无礼义矣。”[16]批评黄子洪的心在性外、心出于性说割裂了心性关系,作为性之内容的五常皆根于心,故性在心内,“心出于性”则导致心丧失了义理内涵,仅仅成为知觉虚明之心。在“明德”的讨论中他亦主张心即性、性即心的心性为一说。《复杨志仁书》说:
此但当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今观所答,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
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则仁又便是心。《大学》所解明德,则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17]
解答明德究竟是性是心的疑问,应从心性为一的角度着眼,批评杨志仁说导致心性为二。心与仁具有分合关系,既有各自为二,不可合一的情况,如颜子三月不违仁;亦有心即是仁的合一情况,如孟子仁人心说。“明德”则是心性即一的概念。勉斋特别突出了“心即仁也”这一心与仁相合的向度,在分析仁的内外宾主之辨即提出“以义理言,则心即仁也。……其旨尤切”。弟子双峰指出孟子“仁人心”与“求放心”之心皆应指义理之心,批评《集注》从知觉之心理解“求放心”,与“仁人心”说不相应。勉斋认同双峰说,提出心有义理、知觉两面,其中又存在专指一面和合指两面的情况,故心性之分合说需具体分析,“心字有专指知觉一边而言者,有专指义理一边而言者,有合知觉义理而为言者。须逐处看得分晓”。勉斋还提出“非性情之外别有心”说[18],意在强调心与性情并非为二,心就是性情,是性情中对之起主宰作用者。
勉斋指出,重章句与重存养的朱陆两家工夫主导学界,二者“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各有优劣。在一般意义上,勉斋主张讲学、存养不可偏废,此即朱子合尊德性、道问学为一的立场。《复饶伯舆》言,“守章句者不知存养之为切,谈存养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缓,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卒无得焉”[19]。但因药发病、矫正学弊是决定勉斋工夫立场的关键因素,有见于朱子学者易于偏向章句讲学,缺乏身心存养,勉斋反复呼吁学者工夫当从以讲学穷理为主转移到身心上来。存养决定了致知之效,无存养,致知将流入讲说文字的口耳之学而毫无益处,说“须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论辞章,恐终不济事也”[20]。
“检点身心”。勉斋反复论及学问根本就是治心修身。“学问之道,治心修身而已。”在给双峰信中指出,古人之学在身心用功,以检点身心为主,讲学穷理为辅。透过格物穷理与检点身心工夫的对比,突出检点身心工夫的主导地位。《复饶伯舆》言:
近亦颇觉古人为学,大抵先于身心上用功……无非欲人检点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故初学之法,且令格物穷理……亦卒归于检点身心而
已。年来学者,但见古人有格物穷理之说,但驰心于辨析讲论之间,而不务持养省察之实……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寻行数墨,入耳出口,以为即此便是学问,……则虽曰学者之众,而适足以为吾道之累也。[21]
就往古圣贤用功之语来看,如尧舜精一之传、文王心事之制等,皆是检点身心工夫。钻研圣贤经典的格物穷理之功,是为了探究为学之方、获得正确义理,以做到居敬集义,最终归于检点身心。检点身心是格物穷理的目标所在。为此,勉斋严厉斥责学者放荡身心,埋头义理辨析之中,丧失了操存涵养自我反省的身心工夫,流于言行背离的口耳之学,走向了圣人之教的背面。痛切指出,讲学穷理人数虽众,却不仅无益于道之传承,反而会伤害之。强调检点身心而非格物穷理,才是道之传承的根本所在。为此,他强调持养省察工夫与讲学穷理的区别,批评饶鲁将二者合说有误。
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皆务外者也。……居敬集义乃是要检点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晓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
可合而言之也。
既然圣贤教人工夫皆是检点身心,故学者为学用心,自当以持养省察、敬义夹持工夫为主,讲学穷理乃辅助涵养省察工夫者,为学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仅仅追求讲学穷理,则是向外为人之学,而非切己向内之学。敬义工夫要求在念头思虑上用功,通过持养、省察双向并进之方,达到内直外方之效用。敬义是检点身心的实践工夫,格致是探究事理工夫,二者所主不同,应严格区分而不可混为一体。在与李燔的信中,他亦将检点身心与讲学穷理对立起来,痛斥流于讲学是儒道失传的罪魁祸首,强烈表达了应以身心点检为主的思想。《与李敬子司直书》言:
近读《中庸》,因推考古先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博文易而约礼难。后来学者专务其所易而常惮其所难,此道之所以无传……若
但务学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学问也。……独南康德契兄与诸贤维持,讲学最盛……但不知于身心上点检处如何耳。[22]
古代圣贤之学皆是就身心用工,如《书》之人心道心、《易》之直内方外,皆是论身心工夫而非讲学。夫子担心学者认识倾向一偏,故以博文与约礼对举,希望兼顾讲学之文与实践之礼。就先后论,博文在约礼之前;就难易论,约礼更甚于博文,而学者流于外在讲学而放弃了约礼工夫,直接导致道的失传。当以戒惧慎独工夫为补救之方,以之为毕生事业而时刻遵循,讲学穷理不过起讲明戒慎的辅助作用。如仅知讲学则丧失了学问根本,学问根本在于身心实践。南康虽然为目下师门讲学最盛之地,更应用功于身心检点。
勉斋反复指出检点身心的意义,以极为强烈的对比性措辞强调是否有检点工夫是人生分界所在。“不到此间议论,虽杀人放火,自不相干;既到此间议论,须是检点自己,从头到尾,得彻方是。”[23]晚年屡屡道及检点身心是人生唯一重要之事,百事皆当放下,唯独检点身心工夫不可丝毫放松。“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检点身心为急也。”[24]只有检点身心才能使人性光明、纯粹、洁净如初,而恢复本初,不负此生。“今亦他无所用心,只得检点身心,令明净纯洁,交还天地父母耳。”[25]
勉斋非常重视孟子的“求放心”说,认为此是极重要的身心工夫,提出“存心之学”与辞章记问之学的区别。人心受到物欲拖累,就会放荡奔跑,从而丧失天理之约束,故圣贤以战战兢兢的静存动察工夫,来确保本心的存在。孟子求放心说是对学者提出的真切警诫,事关儒家之道的传承,秦汉以来学者沉溺于辞章、记问之学而丧失了古人存心、求心之学,直到周程先生,方才接续道统。学者于动静寝食中,皆当时刻牢记“求放心”而不可须臾偏离之,此为读书穷理之根本。“且是以‘求放心’为本,一动一静、一寝一食,不可离此三字,便有以为之根本,然后可以读书玩理也。”[26]多次告诫学者读朱先生书,应加倍于求放心工夫,反复批评过于思索文义的行为。强调自家心灵是书本文义的主宰,不能以书本之说漫过身心,提出“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说,此与象山“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说精神颇有相通。并多方设法,诱导学者反归于求放心。
先生曰:“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可也。”又尝言,“学者役精神于文义而不反求诸心,终未免有口耳之学。”故于讲论之际,必宛转而归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27]
勉斋亦强调存念头的重要。指出作为工夫之首的戒惧,具有自然、简易、内在、当下的特点,一念即是,不待他求,不待外索。直接将之简化为当下一念,这与心学的当下说相通。《复黄会卿》言,“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28]如能存心,则念头存而不失的当下,万理皆在。“存心则一念存,万理具”。帝王之学亦不过是通过检束、防制其心,使念头皆合乎中道。穷理玩索工夫未能专注精一,原因在于“反身一念”未能做到。而贤愚之分的关键亦在于为学念头是在身心之内还是在其之外。
勉斋尽管凸显了心的本体义,推崇反身向内的“求心”工夫,但并未走向象山“心学”,而是坚持并发展了朱子学的主敬立场。为学首要是检点身心而非读书,检点身心之首则是持敬。“为学须先理会心,理会心先须持敬。”[29]主敬不仅是求放心之要旨,更是必须牢记于心、须臾不可离的“护身符”,是学者为学的必备之方,是儒家抗拒一切鬼魔上身的救命符。“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便是护身符。”[30]
勉斋身心内转之学,得到后人的继承认可。吴昌裔指出,勉斋以居敬集义为主的身心点检向内工夫,是对文公之学的进一步推阐。“先生体贴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是则文公有功于程氏,而先生有助于师门。”[31]勉斋“内转”之学在弟子双峰那里得到弘扬。除批评朱子“求放心”章对“心”的理解析为义理与知觉外,在牛山之木章双峰又提出同样的批评。双峰之学体现出追求合一、简易之学的特点,多处批评朱子之解过于分析,如批评朱子将“诚”与“道”析为“本、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等说过于支离;以知行交互解三达德又“头绪未免太多”等。
朱陆异同是朱子后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北溪表现出极力捍卫师门、抨击象山的态度,勉斋对陆学态度相对温和,认为其最大问题是“不读书”,但勉斋自身对读书的态度又颇矛盾,认为只是第二义,第一义是持敬收心,批评“后生辈皆以为读书者,充塞时文之具矣”[32]。双峰虽亦不满于象山不读书说,却提出“尊德性以为之本”说。如何看待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判定朱陆学者立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双峰后学的吴澄则更因力倡“尊德性为本”而被视为陆学,成为元代朱陆合流的代表。其中虽不无误解,但自朱子格物穷理到勉斋“点检身心”再至双峰、草庐“尊德性为本”,确乎显示出“后朱子学”演变的某种真实轨迹和趋向。
勉斋《论语》诠释,体现出对朱子学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重趋向,奠定了“后朱子学”经典诠释的基本样式,弘扬了朱子学的理性辨正精神,指引了朱子学转向内在身心的工夫路线,昭示了日后朱陆异同话题的彰显,对深入研究朱子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近思录专辑》简介
方笑一
众所周知,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是儒家自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宗师。作为其思想之承载,朱子著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朱子与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最受后世关注,被誉为“六经、四子之阶梯”“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在中国以至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历代学者或注解研习,或订补递修,创作过数量庞大的“后近思录”,这些文献是《近思录》学术史的载体,也是朱子学发展、传播史的一个缩影,在古籍版本、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各方面都具有巨大价值。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分设“《近思录》后续研究著述”子课题,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后近思录”凡二十一种,细致校勘,精心标点,是为《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近思录专辑》。
作为《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第一个专辑,交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思录专辑》,不惟内容精优,形制典丽,更将为《近思录》学术史专题研究提供最基本、可采信、成系列的文献资料库,对朱子后学思想、宋明理学乃至泛中华文化圈历史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近思录专辑》总目
第一册[宋]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
[宋]叶采近思录集解
南宋衢州学宫刻本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注解语录六百二十二条,是《近思录》注本中现存最早的宋刊本。半叶九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十七字,左右双栏,有界行,白口,顺鱼尾。杨伯嵒衍注时,拟定了十四卷卷名,注文多引用孔子、孟子、伊川、南轩、朱子、吕东莱等诸子之语要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注释,与历史上南宋叶采《集解》同中有异,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本次校点整理以北京大学藏本为底本。
南宋朱熹再传弟子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注解语录六百二十二条,成书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现存元刻本三种,或残缺或补修或抄配。明清时叶采《近思录集解》刻本繁多,盛行于世。本次校点整理以清初邵仁泓校刊本为底本,以元刻明修本为校本。叶采集解《近思录》时,根据各卷的主旨拟定了篇名,为后世《近思录》注释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纲领,叶采所拟篇目几乎成为一种范式,也成为后世续编、仿编者重要的参考纲目。叶氏注本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是历史上东亚学界非常尊崇的文本,影响久远。
第二册[宋]陈埴 近思杂问
[宋]蔡模 近思续录
[宋]蔡模 近思别录
[宋]佚名 近思后录
[明]江起鹏 近思录补
南宋朱熹再传弟子蔡模《近思续录》十四卷,是蔡模编纂朱熹语录四百三十八条而成,主要选自朱熹《文集》《语录》《易本义》《书传》《论语或问》《太极图》《论语集注》等。本次校点整理以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底本,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清柯崇朴校订,天盖楼藏版,嘉兴图书馆藏。以日本宽文八年(1668)刻本为校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该仿编本对后世东亚《近思录》续编、仿编者影响很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
南宋无名氏《近思别录》十四卷,据校点者考证认为是蔡模所为。蔡模此编采集朱子两挚友张栻与吕祖谦的语录共计一百零八条编纂而成。现存最早的藏本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宽文八年(1668)刻本《近思别录》,本次校点以此本为底本。它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第三册[清]张习孔 近思录传
[清]李文炤 近思录集解
《近思录传》十四卷,清张习孔撰。张习孔(1606~?),字念难,号黄岳,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于江都。父张正茂,善诗古文,有《元晨诗集》。习孔十一岁丧父,家道中落,无资求学,“然性好书,史、鉴、百家暨诗赋、稗野间有所觏”(《宗雅集叙》)。为诸生十年,于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官刑部郎中,九年(1652),官山东提学佥事,仅数月即丁母忧,“见世途崄巇,绝意仕进,家食十余年”(《家训》)。晚年侨居扬州,筑诒清堂。据本书自序,康熙十七年(1678)仍在世。习孔学术通博,贯于四部,著有《大易辨志》二十四卷,《檀弓问》四卷,《云谷卧余》二十卷、续八卷,《诒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另有《家训》一卷,《系辞字训》一卷,《七劝口号》一卷,《使蜀纪事》一卷。其中《云谷卧余》《诒清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据《近思录传》自序的落款可知,本书的最后编定时间为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然序中自述作者少时便受读《近思录》,“喜其约而备,微而显,昕夕玩诵,意有所会,辄不自揆,敬为传数行,附缀本文之下,以相发明,序次篇章悉本朱子之旧,日诠月徙,积成篇集”,可见本书的编纂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又据序中所云“自甲寅编定以来,又已数易其稿”,则初稿编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后又经修订,方成定稿。关于本书的编纂目的,作者在自序和凡说中皆有交代,一是不满于明人周公恕“取叶氏本参错离析之,先后倒乱,且有删逸”“创为二百余类,全失朱子之意”,欲恢复《近思录》一书的原貌,所谓“保其故物,无使紊轶”;二是作者也想将其长期阅读近思录的体悟记录下来,传之后世,所谓“微志窃同夫朱子”。故而,作者编纂本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无论我们对其内容做何评价,本书都是后世研究张习孔学术思想与近思录诠释史的一部重要文献。本书对《近思录》的诠释,主要着眼于义理的阐发,而非文字的训释,作者时常表露自己对于近思录所涉议题的种种看法,如云“善风俗,正人心者,全在上耳”(卷七《出处篇》),这是对当权者提出要求;又云:“国家之坏,由官邪也。今方能饰治而振起,则尊高洁之志,以励天下之廉耻,使不至于复坏。”(同上)这则是为治理腐败提供药方了。应当说,这些论述对后世颇有启迪。本书的版本,目前所知的仅有上海图书馆藏清诒清堂刻本十四卷,此本黑口,单鱼尾,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每卷首署作者名外,并署“男潮、渐同校”,为张习孔家刻本。末卷“殆亦与此意近”以下阙,故为残本。今以此本为底本加以校点整理,正文校以上海图书馆藏明吴邦模刻《近思录》白文本。由于本书为孤本,因此整理出版对于研究理学史和清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册[清]张伯行近 思录集解
《近思录集解》注家很多,此书注解颇遵叶采,偏于义理发微,且用语明白晓畅,疏解务于精细,令人难生歧义,一向受到清代理学家和各地学堂、书院学子的推崇,故有清一代,屡有刊刻,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伯行《近思录集解》的版本众多,学界多以乾隆元年(1736)尹会一重刻本最为嘉善,学者也多以此书为整理和研究对象,如张京华的《近思录集释》等书。但据各种著录,与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尚存天壤之间,最后几经周折,从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初刻本。经认真比对和研读,发现初刻本较尹会一重刻本多出40余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次整理,第一次以东京大学所藏初刻本为底本,校以尹会一重刻本和马氏存心堂刻本。因底本和校本的完备,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定本意义,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
第五册[清]张伯行 续近思录
[清]张伯行 广近思录
《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清张伯行辑。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学者称“仪封先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后入值南书房,由户部侍郎擢礼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卒于官,赐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张伯行学宗程朱,笃信谨守,躬行实践,居官清廉刚直,清圣祖称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世宗曾钦赐“礼乐名臣”四字褒之。
自《近思录》编订行世以来,由于其作为理学经典文本和入德之门的重要地位,备受后世儒者的推崇和重视,历代注解诠释之作层出不穷,而依仿续编之作亦蔚为大观,张伯行所辑《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即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张氏于《近思录》极为服膺,以为其书“体用兼该,义理条贯”,学者由此问途,方可望见先圣门墙,进而深入堂奥,故对其详加诠释疏解,撰成《近思录集解》,后又相继纂成《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十四卷,凡六百三十九条,皆采辑朱子之语,并为之疏解。《广近思录》十四卷,凡一千二百十七条,每卷依次采择宋张栻、吕祖谦、黄榦,元许衡,明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七家之言。二书分卷门目仿诸《近思录》之例,所采录条目皆依据“关于大体,切于日用”之标准。据张氏自言:“余于《近思录》所为既诠释之而又续之,既续之而又广之,冀有以章明义蕴,引进后人,而且以辅翼儒书于不堕也”,“学者诚由《近思录》而并及夫《续》与《广》二录,寻绎玩味,沉潜反复,万殊一理,悠然会心,然后六经四子之书不为日耳,当必有身体而心验之者,入圣之阶梯无逾斯矣”。是为其所以纂集此二书之意。从《近思录集解》到《续近思录》《广近思录》,构成一个脉络相承的经典体系,体现了张伯行对程朱理学渊源统绪和论学要旨的认识、提炼和阐扬,对《近思录》的流传和理学的发展皆有积极意义。
《续近思录》《广近思录》今存刻本两种,分别为康熙年间苏州正谊堂刻本(康熙初刻本)和同治年间福州正谊堂全书本(同治重刊本),其中康熙初刻本较为稀见,而同治重刊本流传较广。但同治重刊本其所据之原本内容已有残缺,且校勘不甚精审,故其版本价值远不及康熙初刻本。此次校点整理,我们利用康熙初刻本作为底本,以同治重刊本作为校本,同时广泛参校所引诸家之书,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认真进行文字校勘,准确施加标点符号,精心撰写校勘记,力求形成精审准确的现代通行本,从而为广大读者带来方便。这也是此二书首次系统整理出版,因此该整理本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具有极大出版价值。
第六册[清]黄叔璥 近思录集朱
清代黄叔璥《近思录集朱》十四卷,稿本,现仅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成书于1754年,作者将散见于《或问》《语类》《大全》《文集》内的朱子言论,裒辑荟萃,附于《近思录》正文下。此外,还汇集了先贤,朱子的好友、门人、后学等著述中可发明《近思录》的言语,堪称续、广《近思录》诸书中“以朱释朱”一巅峰之作。此书因为是未竟稿,堪称稿本信息著录之集大成者,是从事版本、校勘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可不研读的精品。目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子海珍本编》据国图所藏稿本影印收录此书。迄今为止,还未见有关此书的校点整理本问世。整理出版此书,应该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第七册[清]茅星来 近思录集注
朱熹《近思录》是一部指导初学入门的理学启蒙书。《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是对《近思录》的详细注释,清茅星来撰。茅星来(1678~1748)字岂宿,浙江归安人。他极其推崇朱子的学说,因对于当时坊间流行的叶采、杨伯嵒《近思录》注释不满意,“病其粗率肤浅,解所不必解,而稍费拟议者则阙,又多彼此错乱,字句讹舛”。故此,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有以下特点:一:博采众说,参以己见。“取四先生全书及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二:名物训诂,考证尤详。“其名物训诂,虽非是书所重,亦必详其本末。”后人以为,开清人以考据方式注解《近思录》之风尚,并为乾嘉时期江永的集注《近思录》导乎先路者,即茅星来。其《近思录集注》亦为清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之一。
第八册[清]施璜 五子近思录发明
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是朱熹、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的一个重要衍生品。《四库提要》介绍朱熹、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云:
臣等谨案:《近思录》十四卷,宋朱子与吕祖谦所共辑。盖周、张、二程之书,宏深奥衍,承学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虑其不知所择,因与祖谦分类辑纂,以成是书。书以“近思”名,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论者谓为《五经》之阶梯,信不诬欤!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后因有续而广之者,亦堪辅翼,而权舆之精,无过是编云。
由此可知,在朱、吕合辑的《近思录》中只有四子,没有朱熹。《近思录》由四子变为五子,肇始于清初的汪佑。汪佑也是休宁人,学者称为星溪先生。施璜在《五子近思录发明序》中记此事云:
(朱子)尝谓学者曰:“《四书》者,《五经》之阶梯;《近思录》者,《四书》之阶梯。”夫阶梯也者,言所由以从入之序也。然则《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则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则不可以言《四书》也明矣。虽然,孔子之道自孟子后失传者一千四百余年,至周子、二程子、张子而始着,至朱子而始大着。夫既集周、程、张四先生之言为阶梯,若不得朱子精粹切要之言合观之,则学者终有所缺憾。故星溪汪子(按:即汪佑)将琼山先生所著《朱子学的》,与梁溪先生所著《朱子节要》合编之,以续于周、程、张之后,《近思》于是为完书,而阶梯之说亦于是为详备矣。
实事求是地说,汪佑《五子近思录》超过了朱、吕合辑的《近思录》。为什么?因为讲宋明理学而没有朱熹,缺了主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从数量上来说,朱、吕合辑的《近思录》原共六百二十二条,汪佑分门别类予以增补,共增补朱子语录五百四十八条,合计一千一百七十条。
朱、吕合辑的《近思录》,注者多家。而汪佑《五子近思录》尚未有注家。施璜是《五子近思录》唯一的注家。施璜的注释不叫注释,而叫“发明”。之所以叫“发明”,是因为施璜的注释主要是采用明代理学家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四家著作中的原话来发明五子的真谛,故曰“发明”。这样的注释方法,近乎清人所说的“以经解经”,说服力更强。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说:“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由此可知《五子近思录》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所占的地位。而要透彻理解《五子近思录》的内容,则《五子近思录发明》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此书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精华,其注释水平亦非今日之今注今译所能遽然企及。考虑到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中所占的地位,为了满足研究宋明理学的需要,则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的出版价值不言而喻。
第九册[清]江永 近思录集注
[清]汪绂 读近思录
《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清江永撰。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号慎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康熙四十年(1701)岁试,补婺源学弟子员;雍正八年(1730)檄升太学,因家计艰难而未赴;乾隆十五年(1750)特诏荐举经明行修之士,婺源县令特往起之,称病且老而谢之;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终年八十有二。江永邃于经学,尤精三礼,兼擅音韵、钟律、步算之学。不止发挥汉学,精擅考据,且能深入宋儒奥窔,研悦而羽翼之,卓然为当世大儒。
《近思录集注》的特点:一是仍《朱子遗书》原本《近思录》次第,恢复旧貌;二是“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集注》既出传世,即为编修四库全书收入,馆臣称其“引据颇为详洽”,“亦具有体例,与空谈尊朱者异也”。儒林学界,并多赞誉,谓之“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至为精切”,“比类发明,条理精密,不特不敢轻下己见,并不敢杂以他儒之议论,俾后之学者一意遵朱而不惑于多歧”云云,以为“自叶仲圭集解以下注释者数家,惟此最为善本”。是以,后世屡屡重刻再造,成为清中期以降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
第十册[清]刘源渌 近思续录
钱穆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宋代理学三书随札》)正是由于《近思录》这种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后世出现了不少与其相关的书。其中清初理学家刘源渌的《近思续录》,便是颇有特色的一部著作。此书因朱熹《近思录》篇目,采辑朱熹《文集》《语类》《或问》精粹分门编辑,分内外两篇,以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为修己之本,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异端、圣贤为治人之事。据刘源渌门人陈舜锡、马恒谦所作序,为编此书,刘源渌沥尽心血二十余年,意在以此书为《近思录》之阶梯。
第十一册[清]陈沆 近思录补注
[清]郭嵩焘 近思录注
[清]吕永辉 国朝近思录
《近思录补注》十四卷,清陈沆撰。陈沆(1785~1825),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年四十一卒。陈沆以诗文饮誉当时,《近思录补注》是其唯一的学术著作。
自《近思录》问世以来,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其中以江永《近思录集注》最为著名。《近思录补注》则基于江永《近思录集注》而作,全书对江永《集注》多有因袭取舍。其注解之特色,是略于训诂考证,亦不重诠解文义,而重在采辑后儒之说,借以阐明本文旨意。注文所引以朱子之说为主,与江永《集注》性质相似,具有“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特点。此外还广泛采择自宋至清诸儒之说,间亦附有陈氏本人的案断发明。
《近思录补注》是比较重要的《近思录》注本,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相较而言,江永《近思录集注》很多条目的注解比较简略,有些甚至没有注文,而《近思录补注》则广征博引,荟萃众说,补入大量注文,注解更为详密。作为晚出之《近思录》注本,《近思录补注》充分汇集前人成果,对叶采《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等,亦皆有借鉴参考,而其所引据诸儒论说,总数不下七八十家,其中不乏具有重要价值者。如所引魏源之说十一条,魏源文集中均不见记载,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又引秦氏别隐之说三十八条,其姓氏著作皆隐而不彰,录存秘逸,洵属可贵。《近思录补注》之价值意义,即此可见一斑。
《近思录补注》今存钞本一种,系陈氏原稿,现藏湖北省图书馆,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刻本有多部,藏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等处。迄今为止,《近思录补注》尚未经校点整理,对其流传和研究是重大缺憾。因稿本多有增删修改和墨笔勾画之迹,很多字迹难以识别,而刻本数部庋藏于图书馆,流传亦不甚广,对普通读者而言实不便于阅读。此次校点整理,我们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精心选择底本和校本,认真进行标点和文字校勘,力求提供一部精审准确的现代通行本,从而为读者带来方便。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周惇颐墓
——其历史与现状
〔日〕吾妻重二 傅锡洪译
前言
北宋的周惇颐(1017~1073)是近世东亚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他的揭示宇宙生成与构造的《太极图·图说》,不拘泥于俗务的“胸中洒落”的高雅精神,以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圣的“圣人可学论”等等,都无不因其蕴含深刻的思想和崭新的内容,而被南宋的朱熹(1130~1200)吸收从而构成朱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周惇颐的思想与品格对其后的中国以及韩国、越南、日本等所谓“儒教文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笔者在旧作中已有论及。[1]
笔者于2011年10月19日至20日参加了一次国际朱子会议并发表了论文[2],这次会议是在与朱熹渊源极深的,位于江西庐山山麓的白鹿洞书院召开的。会议结束后的10月21日,笔者得以拜访了周惇颐墓。[3]
周惇颐的墓位于庐山北部的九江市南郊。在历尽沧桑之后,如今已经整修得气势恢宏。本文即欲对其曲折的历史以及现状进行考察。它近来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情况。
另外还须交代的是,本文使用的周惇颐文集是十二卷的南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的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八八,书目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南宋版《文集》”。
一、周惇颐墓
周惇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天禧元年(1017)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他因恩荫入仕,但始终与权力中枢无缘,而是作为地方行政官迁转于江西、湖南、四川和广东等地,并取得政绩。这期间,在南安军(今江西南部)他教授了少年时代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熙宁四年(1071)八月初,已经五十五岁,步入迟暮之年的周惇颐出任位于庐山东面的南康军的知事,但他随即隐退,住进建于庐山北部莲花峰山麓的“濂溪书堂”,并在那里度过了晚年。熙宁六年(1073),周惇颐去世,享年五十七岁。[4]
周惇颐的墓建于“江州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的三起山。[5]如后所述,这个墓区是由清末光绪年间所扩大和整修而来,清代当时的地名是“九江郡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栗树岭”(栗树岭即三起山),位于庐山莲花峰以北20里,即现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周家湾。
饶有趣味的是,埋葬于此的除了周惇颐以外,还有他的母亲郑氏、他的原配陆氏以及继室蒲氏,为四人的合葬墓。接下来本文就考察他们四人先后埋葬于此的经过。
1.母亲郑氏(仙居县太君)。周惇颐的母亲郑氏是郑璨的女儿,郑向的妹妹,她嫁给了周惇颐的父亲周辅成。周辅成是特奏名赐进士出身,天圣九年(1031)卒于贺州桂岭(今广东北部)令任上,葬于家乡道州营道县。十五岁便成为孤儿的周惇颐,跟随母亲寄身于舅舅郑向门下。郑向是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任过知制诰,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成为杭州知事的高官,周惇颐入仕也是受其恩荫。不过在周惇颐母子投靠五年之后的景祐三年(1036),郑向便在知杭州的任上去世,死后葬于润州丹徒县(今江苏镇江)。接着,次年景祐四年(1037)七月郑氏于五十五岁之际去世,死后葬于郑向的墓旁。
然而后来润州的墓因为水害而损毁,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十六日,刚刚就任南康军知事的周惇颐特意将母亲郑氏的遗骸移至庐山,将其改葬于现在的墓地。潘兴嗣在《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南宋版《文集》卷八)中详细记载了此事。
此外,关于母亲郑氏的改葬,度正在其《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南宋版《文集》卷首,以下简称《年表》)的“熙宁四年”条目中有如下的记载:
俄得疾,闻水啮仙居县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军。十二月十六日改葬于江州德化县清泉社三起山。葬毕曰:“强疾而来者,为
葬耳。今犹欲以病污麾绂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
另外潘兴嗣的《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在叙述郑氏葬于润州之后接着记载道:
后二十年,水坏墓道。惇颐以虞部郎中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乞知南康军。遂迁夫人之衬窆于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也。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周惇颐乞知南康军不外乎是为了将母亲改葬到庐山。尤其是《年表》中所说“强疾而来者,为葬耳”,可以让我们强烈意识到这一点。
而《仙居县太君墓志铭》的说法则略有不同,患病、乞知南康和改葬母亲这一连串的事情具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年表》最后“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说的是周惇颐辞去南康军的职务,转而担任南京应天府的分司官。分司官即便不担任实际职务也可获得一定俸禄,乃是官员将要引退之际担任的闲职官。[6]这也意味着周惇颐就任南康军仅仅四月有余。由此可推知,患病后的周惇颐考虑在自己所酷爱的庐山隐居下来[7],安静地度过余生,并希望将母亲的墓安置在其旁边。母亲郑氏在丈夫去世之后艰难地将周惇颐抚养成人则已如前所述。
而郑氏在去世后获赠“仙居县太君”的称号,依照的则是北宋当时对文武百官的母亲以及妻子实行的叙封制度。[8]
2.妻子陆氏(缙云县君)。正室陆氏是职方郎中陆参的女儿,在景祐三年(1036)周惇颐二十岁时嫁给他。陆参的生平已无从考证,职方郎中是相当于从六品的小官,他的其他传记资料也没有留下,由此或可推知他的一生并不显赫。陆氏为周惇颐生下长子周寿,于嘉祐三年(1058)周惇颐四十二岁的时候去世。[9]
3.妻子蒲氏(德清县君)。继室蒲氏是蒲宗孟的妹妹。蒲宗孟比周惇颐年少十岁左右,是皇祐五年(1053)的进士,后任翰林学士,并于元丰五年(1082)高升至相当于副宰相的尚书左丞,但仅仅一年后就左迁汝州知事,在辗转担任多地知事之后,卒于知大名府(今河北南部)任上。嘉祐四年(1059),由于景仰周惇颐的品行,蒲宗孟将妹妹嫁给了他。其时周惇颐四十三岁。蒲氏为他生下次子周焘。蒲氏于何时去世并不清楚,从蒲宗孟《先生墓碣铭》[10]称“德清县君”可知她在周惇颐之前去世。
我们并不清楚周惇颐的两位妻子是何时被合葬在一起的。不过就陆氏而言,她去世时,周惇颐正以合州(今四川)签曹判官厅公事的身份赴任四川。她可能被暂时埋葬于某处,熙宁四年(1071)以后再移葬于此。
4.周惇颐。如上所述,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惇颐五十七岁时去世。随后十一月二十一日按其遗言,他被葬于母亲郑氏墓左侧,一如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所记载的:“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母大人之墓左,从遗命也。”葬于母亲墓侧的遗言较为罕见,由此也可看出周惇颐对于母亲的深情。
二、对周惇颐的表彰及其墓的修复
1.南宋
南宋建立后不久,周惇颐便受到了朱熹、张栻(1133~1180)等以道学士人为中心的群体的推崇,对其的某种“表彰运动”也由此开始了,尤其是淳熙年间以降更为显著。道学家们竞相在与周惇颐渊源颇深的地方的州县学或书院里奉祀他,借此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正当性的根据。这些从南宋版《文集》和《濂溪志》为数众多的《祠记》《祠堂记》中便可窥知。以下举出其中几个显著的例子。
如淳熙二年(1175)冬,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詹仪之在韶州曲江县(今广东省)建立周惇颐祠之际,张栻为其撰写了《祠堂记》。[11]同年,静江府知事张某在府学的明伦堂之侧建立“三先生祠”,张栻也为其撰写了《祠记》。[12]“三先生”即周惇颐和二程。上述祠堂均供奉有周惇颐的画像。淳熙五年(1178),张栻还为周惇颐出生地道州营道县(舂陵)重修的祠堂撰写了《祠堂记》。这所祠堂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兴建的祠堂基础上重修、扩建而成,据称达到了“堂四楹”的规模,堂中央供奉有周惇颐和二程的画像。[13]
而在江州(九江)的庐山山麓,江州知事潘慈明与通守吕胜己于淳熙三年(1176)重建了濂溪书堂。濂溪书堂原为周惇颐的住处,当时已经荒废。重建的翌年即淳熙四年(1177)二月,朱熹为此写了《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文中写道:
先生姓周氏,讳惇颐,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渓,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记之。[14]
此后,朱熹每当读到周惇颐之书便想要拜访江州和庐山,对周惇颐的为人仰慕备至。
两年后的淳熙六年(1179)三月,他成为周惇颐曾担任过的南康军知事,由此得以前往江西,实现上述愿望。四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建立周濂溪祠,供奉他的画像,并以二程配享。朱熹《文集》中的《奉安濂溪先生祠文》即为那时所读的祭文。[15]张栻也为此寄来了《祠记》。[16]此外,据记载朱熹在此期间踏访了周惇颐的遗迹,由此可推断他应该也到过周惇颐墓。[17]五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刊行了周惇颐的《太极通书》[18],十月,复兴了白鹿洞书院。[19]
这样,南宋中期道学家们的表彰运动极大地突出了周惇颐的存在。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应魏了翁等人的请求,周惇颐被朝廷赐予“元”的谥号。[20淳祐元年(1241),南宋朝廷将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并追封周惇颐为汝南伯。[21]不用说,这意味着始于周惇颐的朱子学(道学)的系谱亦即“道统”的确立,周惇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在这前后,嘉定十四年(1221),朱熹门人度正收集周惇颐的遗文编成《文集》。[22]至于墓,则在端平元年(1234)得到修复,并设置了祭田。[23]宝祐元年(1253),在墓右侧筑室,并置周惇颐像于其内。[24]
2.从元明清
对周惇颐表彰的势头在元代以降依然持续。元代延佑六年(1319),加封周惇颐为道国公,明代正统元年(1436),修复其祠堂和墓地,并给予其后人以恩惠。[25]
弘治三年(1490),九江府知事童潮修复杂草覆盖的墓地,在墓前修建三间祠堂,安置周惇颐的像,并挂上“宋元公濂溪先生祠”的匾额。另外设立“爱莲室”三间,在其前面开凿池塘,种植莲花,并设立了祭田。[26]弘治十六年(1503),江西督学副使邵宝将祭田扩大,并将周惇颐后代周纶从道州迁来管理祭祀。[27]正德六年(1511),傅楫修复了墓地和祠堂,并增置祭田。[28]紧接着正德七年(1512),廖纪拨出“公廪陶甓数万”,用了两个月时间修葺了墓区。[29]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修复中,则刻上了“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的文字。[30]
清代咸丰五年(1855)二月,罗泽南与李续宾修葺了墓地。[31]罗泽南(1807~1856)是湖南湘乡县人,在太平天国军兴之际,他组织的乡勇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主力部队,他也以此闻名。在九江附近激战之余,他拜访了周惇颐的墓地,并命人将其修复。他虽然身为武将,但朱子学的修养却很深,而且著述颇丰。李续宾是其部下和同乡。[32]他们同为湖南的出身,无疑有意表彰乡土先贤周惇颐。
总而言之,自南宋至清代,历代王朝和士人乡绅对于周惇颐墓的维护和修复,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三、清末光绪年间的整修
周惇颐墓的整修,以彭玉麟及其部下在光绪九年(1883)完成的大规模扩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彭玉麟编辑的《希贤录》对此进行了记载,本文以下主要据此进行叙述。
《希贤录》刊本共上下二卷,上卷二十二叶,下卷十四叶,内题下有“衡阳后学彭玉麟谨辑”,并有光绪九年(1883)春三月彭玉麟的序文。在卷首《濂溪墓图》所附的《说》中,写着“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可见该书是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秋天到冬天期间刊刻而成的。各卷末写着“桐城存之方宗诚/善化麓樵胡传钊分校”“正江与吾李成谋/益阳燕山丁义方合刊”。[33]另外毋庸赘言,《希贤录》这个名字来源于周惇颐《通书》中“士希贤”一语。
编者彭玉麟(1816~1890)是湖南衡阳人,又名玉麐。他与前述的罗泽南都是湘军武将,他在曾国藩领导下创建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屡建战功,官至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并制定了湘军水师营制。光绪九年(1883)编辑《希贤录》之际他已是任职兵部尚书的高官。
丁义方是湖南益阳人,李成谋是湖南芷江人,两人均是彭玉麟麾下的武将。光绪九年(1883)丁义方是湖口镇总兵,李成谋是长江水师提督[34],胡传钊是江西新昌县知县[35]。方宗诚是安徽桐城人,《汉学商兑》作者方东树的族弟,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与朱子学有着共鸣的学者。[36]
卷首的《濂溪墓图》如图1所示。
附于其后的丁义方的《说》,叙述了此次修复的详情。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濂溪周元公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许,系隶德化县属之德化乡清泉社,地名栗树岭,亦名三起山,即庐阜了髻山西北之分支也。墓虽面莲花峰,而相去二十余里,《廖记》所称窆于清泉社莲花之岑,《罗记》所称墓在浔城东南莲花峰下,皆误。义方始闻德化知县刘君长景之言,得确知元公墓所。暨于光绪辛巳,随侍彭大司马率同正任新昌知县胡君传钊,往谒之,乃定集赀修墓之举,自壬午夏经始,洎癸未春蒇事。计拓垣围长八十余丈,高视旧加倍,深其址,而石累以甓而增厚焉。宰木数十株,周环于内,墓之〓磈原罅也,则规石而封之。前有祠,明季已毁于兵。今且濂溪祠与书院遍天下,复可不亟。遂度祠基,建舍于左右,俾奉守者有栖息,展礼者有斋沐之处。崇高其门,而坊表之,自门至墓,级石为道。旧有碑仍之,新立碑四,中为元公母仙居县郑太君墓,左为元公墓,右为元公配缙云陆县君,继配德清蒲县君墓,皆彭公所敬题。义方则谨摹元公遗像,兼图所爱莲花于石,以表洁而遗芳,庶俾过墓则式者有所宗仰乎。工竣以告彭公,为之记。彭公复以征考文献有系于元公最要者,辑为《希贤录》,命胡君传钊继方存之先生分校督刊。义方亦遵命绘锲《墓图》,且为《说》以附于后。抑更有说者,圣贤道大原无不包,以墓为元公体魄所藏,则任修毋嫌越俎。况有京兆赵将军重修濂溪祠宇之例,在责何敢辞。但不为希贤君子所讥,斯为幸耳。时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
上文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1.厘清了周惇颐墓的正确位置,并指出了廖纪《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和罗泽南《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里记述的错误。
2.“光绪辛巳”亦即光绪七年(1881)彭玉麟率江西新昌县知县胡传钊等前往墓地,并制订对其进行修复的计划。
3.“壬午夏”亦即光绪八年(1882)夏修复工作开始,“癸未春”亦即次年光绪九年(1883)春竣工。
4.围墙长度达八十余丈,高度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一倍,墙基也挖得更深,并在墙顶盖上了瓦,墙体也进行了加厚。
5.种植几十株树木,将周围围起来。
6.在出现了裂缝的坟墓土堆上盖上了切割整齐的石块。
7.墓前原有的祠堂毁于明末的战火,在其左右建立屋舍,以供守墓者休息和祭祀者斋戒沐浴之用。
8.将门加高,且竖立牌坊。
9.铺设从门到坟墓的石板路。
10.在原有石碑的基础上,新建了四块石碑。中央是周惇颐之母郑氏的墓碑,左侧是周惇颐的墓碑,右侧是周惇颐妻子陆氏和蒲氏的墓碑。墓碑表面均由彭玉麟题字。
11.石碑上刻有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以及莲花。
12.彭玉麟将有关周惇颐的主要文献整理成《希贤录》,并命胡传钊、方宗诚等校勘之后将其出版。
13.《希贤录》中,由丁义方画了墓区示意图,并附以解说。
14.在上述引文之外,根据彭玉麟的《重修周子墓碑记》还可了解到,他在原有墓碑题词“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中加上“元公”二字。
由上可见,这是一次规模极大的修复。在竣工后的光绪九年(1883)六月四日,彭玉麟率文武宾客幕僚数十人前往拜谒,并进行了祭祀。[37]
四、常盘大定的调查
彭玉麟整修之后,周惇颐墓的面貌维持了很长时间。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在彭玉麟整修后的三十九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査。他拍摄的照片收入《支那文化史迹》,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情形。
常盘做了如下的记录:
周濂溪墓
江西省九江市南十里铺,有周濂溪墓,其位置在十里铺往左转走大约五里处。穿过横梁上写着“元公周夫子墓”的石门,就是墓地的大门。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其缘由或许在于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登上大门内的石阶,就是周濂溪的墓。周围环绕着石墙,墓前有三块碑,左右有两块碑,周子墓上所刻的内容如下:
濂溪先生像赞
道脉
先贤宋元公濂溪周子墓 光绪癸未
宋赠仙居县太君周子母郑太君墓
宋赠缙云县周子元配陆夫人
德清县周子继配蒲夫人 墓
在将这个墓围起来的石墙的中央,有如下三块碑:
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 嘉靖甲寅
重修濂溪周子墓碑 咸丰甲寅
太极图
笔者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二十八日访问此地的。
常盘当时拍摄的照片如图2、图3所示。
若将这两幅图与图1的《濂溪墓图》及其解说对比,可以看出常盘当时所见的墓地,与后者所记载的光绪时代的情形非常吻合。高大的门以及围墙,覆盖在坟墓上的石块,刻在石碑上的周惇颐像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此外,墓前并立着的三块碑,中间是母亲郑氏的墓碑,左边是周惇颐的墓碑,右边是两位妻子的墓碑。周惇颐墓碑上“元公”二字也是彭玉麟整修后的样子。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也在他墓碑左边(从前面看则在右侧)的碑上。如丁义方解说里提到的,遗像旁边刻着《濂溪先生像赞》,这些都延续了光绪时代的光景。
此外,常盘还提到围墙中央的三块碑,写着“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嘉靖甲寅”和“重修濂溪周子墓碑咸丰甲寅”的两块不外乎就是前述明嘉靖和清光绪时所立的两块碑。这两块碑就是图2左后方嵌入墙体的碑。常盘说周惇颐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但原因并不在于他说的“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而是清末声名显赫的彭玉麟对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整修,才有了这样的规模。
结语:鲁迅、周树人、周恩来及“文革”以后
本文追溯了周惇颐墓漫长的历史,最后对从“文化大革命”至今的情况做一考察。
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笔者留学北京大学期间的1983年5月14日到访了此地。那次漫长的独自旅行的路线是:北京—南京—镇江—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上海—九江—庐山—九江(周惇颐墓)—汉口—北京。根据笔者当时的日记,在从九江市内前往墓地的巴士上,向旅客询问周惇颐墓的情况,得到了“现在就算去的话,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之类的回答,由此引来大家纷纷议论。下了车以后沿着田间小路,朝着像是墓地的方向走去,在洼地中心人工堆放的土就是周惇颐的墓地。周围杂树丛生,建筑物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瓦。如果不向当地人请教,根本不知道这就是周惇颐墓。展现在眼前的风景,与随身带来的常盘著作复印件上的截然不同。询问当地人,他们均说墓是在“文革”中被毁坏殆尽的,笔者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不过从墓地往南远眺庐山的风景,确实非常美丽,当地人对此也都如是说。
不过正如开篇所述,在那以后墓被修复一新。就其经过,以下根据墓地中的碑文《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资料1)加以说明。
周惇颐墓在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文革”中被破坏,只剩下墓穴而已。不过“文革”结束后周氏后裔便为修复而奔走,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会从政府和民间募集到20万元,首先复原了墓冢和围墙等。2004年由其后人出资举办“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设立了“修墓委员会”,委员会向海内外的周氏后人募集约200万元的捐助,在九江市政府支持下,对墓进行了全面的修复,从而恢复了往昔的盛况,整个墓区面积达四千余平方米。(图4、图5)
宗亲会尽可能将墓地复原回彭玉麟当时整修的样子。但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周惇颐母亲和两位妻子的墓碑上都有“公元一九九九年九月日重立”的字样,在母亲的碑左侧的那块碑上,虽然刻着周惇颐的像,但没有了常盘大定照片上“濂溪先生像赞”的文字。只有周惇颐的墓碑上刻着“后学衡阳彭玉麟敬题”的文字,可见这应是光绪时代的原样。此外,背后的石墙上确实嵌入了三块石碑,上面是《太极图·图说》《通书》和《爱莲说》。本来这里嵌入的应是嘉靖年间“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和咸丰年间“重修濂溪周子墓碑”,但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墓区的展览馆里竟然陈列着本文多次提到的潘兴嗣《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并且是刻在石板上的原物。从带领我们参观的许家星那里得知,这是近年从田里发掘出来的。墓志铭原来埋在墓前,可见北宋周惇颐将母亲从润州改葬到这里时,也将墓志铭一起移过来埋藏于此了。这几乎就是周惇颐墓唯一遗留至今的原物,无比珍贵。假如没有“文革”的破坏,这块墓志铭一直埋在地里的话,人们就连它的存在本身都不知道吧。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还有一点,参观了展览馆才知道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以及周恩来均是周惇颐的子孙。挂着“周氏家谱展”匾额的展览馆里,与新的周惇颐坐像摆在一起的有《周氏后裔名人介绍》,其中就包含了上述几人的展区。展出的还有几种《周氏宗谱》。另一个展馆挂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爱莲堂”匾额。现在笔者无暇考证他们的家系,但是他们作为周惇颐子孙的事实应该没有错吧。
因为向来鲜为人知,所以在此提及,希望引起世人的注意。
笔者在此再次惊叹于“文革”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可怕破坏。方宗诚在光绪年间修复周惇颐墓之际提到,咸丰以后战乱频仍,庐山的很多名胜以及佛寺都遭到破坏,而周惇颐墓的树木、石碑以及坟堆等都并未受损,即便是盗贼,也不敢破坏墓地。[39]就算在清末大乱期也保存下来的墓,却在“文革”期间遭到了真正的毁灭。不得不说,即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像“文革”这样无情破坏文化的例子也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在深入推进对传统文化包括儒教的再评价,周惇颐墓的修复也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持。靠近墓的南边的崭新的道路,还被命名为“濂溪大道”。附近还有“九江濂溪宾馆”“濂溪农贸市场”。墓的西边近处有一座于2000年兴办的九江学院,在这所大学偌大的校园里挖掘了一座很大的爱莲池,还立了周惇颐的像。登录九江学院的网站就能看到,这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71年建立的“濂溪书院”(准确说应是“濂溪书堂”),濂溪书院在清末1902年改称九江中学,成为现在九江学院的前身。以上所述,可以说都在诉说着中国正致力于再度“盛世修文”的动向。
资料1《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颂濂溪
——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古今皆然。今重修濂溪墓,以承先人之遗风,夙后世子孙之愿,供仰慕者以瞻。
濂溪墓历千年沧桑,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毁于“文革”、仅存墓穴。“文革”后,族裔周观源奔走四方,呼吁修复。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周国枚、国材、楚阶、汉明等来浔谒祖,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与之连手,以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捐计20万元,完成了一期墓冢、围墙、照壁的复原。2004年苏州鸿利机电设备公司董事长周斌炎出资召开“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成立修墓委员会,由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周楚阶担任委员会主任。他广结善缘于海内外,联同美国侨领周谦益、苏州周斌炎、重庆周厚勇等,共筹款200万元左右,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主任吴宜先积极支持,组织全面修复,终使墓园焕然于世。
濂溪先生,理学鼻祖,图说太极,诠释周易;胸中洒落,光风霁月;道德文章,千古流芳。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今景观已复,而道脉重传,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特为之记以志其盛。
周氏宗亲重修濂溪祖墓委员会
顾 问:吴锦萍 郭建林 周仪 周谦益 周炎沐 周汉彬 周国枚 周国材 周汉明 周振基 周炳树 周国屏 周朝宜 叶伟平
主任委员:周楚阶
常务副主任委员:周斌炎 吴宜先 周厚勇
副主任委员:周黄丽英 周厚立 周开泉 周志峰 叶筱慧 周桂洪 周日新 周镇隆 周锡强
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立
(作者单位: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
杨祖汉
我最近借康德所说的必须对道德从一般的理解进至哲学的理解,才能克服“自然之辩证”,使人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之说,来诠释伊川的从“常知”到“真知”的见解,似乎可以为程朱所以要以穷理、致知格物为工夫,给出一较顺通的说明。而如果程朱所言致知,是对本有的知善恶,即德性之知做进一步的穷究,则由对道德之理之彻底明白,确可起信,而人之私心欲望,自无所容,而不会有借为善而暗中满足私欲的情况出现。而此所谓的“自然之辩证”是人生命中之普遍现象,人必须对治的。若如此解,则致知便有澄清人之意欲,使人不会自欺的功用,如是则致知便可以有诚意的效果,本文拟对此义略做讨论。因对“自然之辩证”义,前已有数文论及,[1]此文从略,而集中在致知乃是对道德义务、道德法则之知及在知道德之理时所会引发的影响上论说。
一、阳明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致知与诚意关系的评论
朱子依《大学》八条目的顺序,认为“诚意”在“格物”“致知”之后,即以“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而他对“致知”的理解是使心知的作用充分发挥,于是“诚意”此一内圣成德的关键工夫是要以对于理有充分的了解为前提,此一诠释固然有《大学》原文做根据,《大学》所说的八条目确是先“致知”才能“诚意”,如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致而后意诚”。故依《大学》,“致知”是“诚意”的根据,意思相当明白。对此一诠释,王阳明做出有力的批评,他说:“纵格得了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了自家意。”[2]阳明认为对于理的认识是知之事,知并不必含行,要在了解了理的意义后,又能依理而行,必须要有另外的工夫,故朱子要提倡敬的工夫,以敬的力量或作用使心依理而行。阳明认为如此理解《大学》并不切于实践,敬的工夫如果如此重要,何以《大学》会把它漏掉呢?[3]故阳明认为“致知”是“致良知”之意,并非推致心知去明理,而是努力推致、实现我们心中本有的良知。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呈现自然有自发的要求朝向天理的方向而实践的力量,依此良知而行就可以有去妄存诚的效果,使我们的现实的生命,成为自发自主地依自己给出的理而实践的道德主体,故若如此解“致知”就可以有“诚意”的结果,工夫在致良知上用,而“致知”就必含“诚意”。阳明之说确是切于实践的,致良知的确当下可以洞开道德行动之源,挺立人的道德主体。牟宗三先生以阳明之说是直贯创生的系统,不同于朱子的横摄系统,分辨十分清楚。牟先生对于朱子由致知而诚意的实践次序的说法也给出了类似于阳明的批评,他认为依朱子所理解的“致知”,并不能达到诚意的结果,若致知是知理的工夫,则从致知到诚意并不能必然相连,故他认为朱子意的诚意,在朱子的理论中是一“软点”[4],即是说朱子意的“诚意”,工夫全在致知上用,而致知是知的工夫,只是知的工夫则不必能开道德行动实践之源。牟先生对朱子意的致知为诚意的先行条件,及“知之者切,然后贯通得诚意底意思”之言,做了以下的批评:
此是以知之真切带出诚意。此固可说。然此种诚意黏附于“知”而见,很可能只表示知之诚,即实心实意去知,不是浮泛地知,真感到求知之迫切,真感到理之可悦而真切地去知,此所谓对于知、对于理、有存在的感受也。……然正心诚意所表示之心意,是道德之心意,是道德行动之机能,而知是认知之机能。求知活动固亦可说是一行动,因而作为行动之源的心意亦可以运用于心知之明之认知而成为真切地去认知,但却并不能限于此而与之为同一。意是行动之源,而实心实意去知、所诚的只是知,此与诚意以开行动之源、这其间毕竟有距离。[5]
另外,牟先生认为,依《大学》原文,诚意的工夫有其独立性,虽说八条目的次序是先致知后诚意,但在《大学》的“诚意章”对“诚意”的解释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并没说“所谓诚意在致其知者”,不同于其他纲目的关系的说法。[6]可知依《大学》此处原文,致知与诚意的因果关系亦可打断,诚意的工夫可以独立地做,此即慎独的工夫。
二、致知是诚意的先行工夫如何可能
依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朱子所说的理是当然之理。[7]我觉得从唐先生的说法可以给出对于理之知可以达至诚意的效果之论据。所谓当然之理或道德之理,只是一理所当然或义所当为之“意义”。即是说对于该行之事,吾人只能够因为此事是该行而行,而不能够有别的存心,此即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所谓道德之理就是“为所当为之事只能纯粹的因为当为而为,而不能有其他存心想法。”此一意义,便应是朱子之致知格物穷到底,要了解的“理”。
如果穷理是穷道德之理,而道德之理只是一对义所当为者,只能为了义所当为而为,不能有其他想法,则此理当然是吾人所本知的,因为此义由人的理性而发,没有人会否认此义。举例来说,为子当孝而且其为孝只能因为孝是当为者,不能因为别的目的(如为了贪求父母财产)而孝。此一意义,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且一定赞成而不会反对,如果你反对此义,就表示说,你认为你的儿女可以因为别的目的而孝顺你,而不是因为孝顺是应该的而孝顺。人绝不会同意这种抱着别的目的而行善,为真正的善行。此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而一旦知道,便会同意,绝不会否定它。如果否定它,就等于是否定了自己按理而给出来的想法,故反对道德之理,会造成反对自己的理性,甚至自我否定的结果,这是不合理的。故如果理以上述的意思来规定,则对于理的认知,是有对于理本有之知来做根据的,此理并无经验之内容,对此理一反思即得,不假外求,根据此本有之知而进一步地求更清楚的理解便是致知,而如果致知是此义,则越致知便会越明理,此是有保证的。而越明理就会越肯定此理、认同此理,越能认同肯定此理,便会真切希望自己能够表现此理或完全地按照此理而实践。[8]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应该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越了解此理,越知其为当然,则人便会越清楚了解此一意义是绝不能反对的。如此,就可以因着了解的深切,而引发人趋向于要求自己做一个纯粹的为了行所当行而行动的人。如此一来,致知当然会造成诚意的后果,知至与意诚之有因果关系可以成立。
这是从明理、知理而引发人要自诚其意的要求,此知理并非从对理毫无所知来开始,因为此理没有别的,只是义所当为或人应只因为当为而为,不能够做当为之事,另抱有别的目的。道德之理只是此义而无其他,则知之并无困难,甚至对此理之知可以说是先验的,因为对此理的了解虽然要通过认知或思辨的活动,但人稍一反省即可知之,而且所知的理都是一样的,即理是普遍的。如此说则此理并不能是由经验提供的,如果是由经验提供,则人不能都能知此理,而且所知的理也会不一样,而对道德之理的知,伊川正式说为“德性之知”,而且说德性之知不假于见闻。[9]伊川此语很明白表示此理不从经验而得之意。此同于张横渠所言“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之区分。[10]朱子虽然对于此德性之知的说明并不太多,但他认为对于理之知是凡人皆有的,依此意也可以说朱子有对于德性之知是人所本有之意,而且是很清楚的。虽然程朱强调必须要通过格物致知才可以对于理有真知,有真知而后能诚意,而如此才能生起相应于道德法则的行动,但不能因为他们这种说法,就认为他们所言之理与心截然为二,理外于心而为心的对象;或心的知理、心之具理是后天的认知地具。此中的关键在于道德之理的特殊性,此意见后文之讨论。
三、引朱子论致知与诚意关系之文献来说明
牟先生《心体与性体(三)》讨论朱子从致知到诚意的工夫进程,引了朱子相关的重要文献,再做批评。牟先生的批评大意,已见第一节所引。但牟先生所引的朱子原文似乎也可以做另一方向的诠释:
1.“‘知至而后意诚’,须是真知了,方能诚意。知苟未至,虽欲诚意,固不得其门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径如此,知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因指烛曰:“如点一条蜡烛在中间,光明洞达,无处不照,虽欲将不好物事来,亦没安顿处,自然着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光之所不及处则皆黑暗无所见,虽有不好物事安顿在后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贵格物,如佛、老之学,它非无长处,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则路径甚明,无有差错,其知所不及处,则皆颠倒错乱,无有是处,缘无格物工夫也。”[11]
朱子所谓的“知得路径”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来规定,故“知至”是从对善恶的“常知”进到“真知”,如果对善恶是本有所知的,则对此从一般的知进至真知,便是对道德上的善恶有透彻的了解,如此,人的私意就不能附着。引文中所说的“然后自然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很能表达在人明白了道德义务是理所当然该行之事,吾人实践义务只能为义而行,不能抱有别的目的时,吾人对此便只能完全同意,不能起别的想法。如果不同意,便是反对自己的理性的想法,也等于是自我否定,此所谓“不得不”。如是则朱子所认为的真知“善知当好,恶之当恶”,便“意不得不诚”之论,是合理的,此中从知至到意诚,是可以以因果关系来说明的。
2.问:“物未格时,意亦当诚。”曰:“固然。岂可说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诚!自始至终,意常要诚。如人适楚,当南其辕。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知未至时,虽欲诚意,其道无由。如人夜行,虽知路从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则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当好,恶之当恶。然临事不如此者,只是实未曾见得。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12]
问者问在物未格时,是否亦要诚意?此问者之意,确如同牟先生所谓的,格物与诚意是可以分开而独立的两种工夫,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打断。朱子对此提问的回应是说,人当然自始至终都要诚意,不能说物未格时,便不用诚意;但若非知至,虽欲诚意,也做不到。朱子此意可表示人本有自发的纯粹地为所当为之要求,故朱子说“岂可谓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辕”。但固然未致知时也须诚意,或人亦会有诚其意之要求,但此时的诚意并不真实,如果不真知善恶的不同,便不能真实地诚其意。朱子此处仍旧对“善之当好,恶之当恶”之知有深浅来说,认为人虽然对善恶本有所知,但临事却往往不能为善去恶,此是因为未曾真正见得实理,若对道理能坦然明白,自然会安而行之。如果朱子所要致知穷理的理是道德之理,则如上文所说,真知道德的理,便会有自己对此理完全认同的效果。而朱子此处言理的确是从“善之当好,恶之当恶”,即道德之理来说。则朱子希望由致知达到诚意的效果,也是有理据的。
3.问“‘知至而后意诚’,故天下之理,反求诸身,实有于此。似从外去讨得来”云云。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原注:厉声言“弗思”二字)又笑曰:“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13]
此段问者之意是说知至而有意诚,是格知天下之理,然后反求诸身,使理实有于己。如果是如此,似是从外而求理,即理非吾人本有。朱子回答强调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厉声说此意。当然朱子的“厉声”之反应可能表示问者所说击中了朱子心理为二的理论弱点;但也可以理解为,朱子认为将其理论理解为理在心外,是很不恰当的,即他这格物致知论并不能被了解为理在心外。固然心是活动的,而理是存有而不活动,二者有不同,朱子所说的心,也不是陆王所肯认的心即理的心体;但虽如此,朱子并不认为理在心之外。理固然不同于心,但对于此道德之理——即“善之当好,恶之当恶”,而且为善是因为善之当为而为——是人一反省就可以知道的,故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在家的儿子与在外的儿子之喻,可以理解为,在心之理与在物之理是一样的,也可以用来区别对此理有常知与真知的不同。
4.问椿:“知极其至,有时意又不诚,是如何?”椿无对。曰:“且去这里子细穷究。”一日禀云:“是知之未极其至。”先生曰:“是则是。今有
二人:一人知得这是善,这是恶;又有一人真知得这是善当为,恶不可为。然后一人心中,如何见得他是真知处?”椿亦无以应。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缓缓寻思,自有超然见到处。”[14]
依朱子意,知至便涵意诚,故他所问的知极其至而意却不诚,当该是知实未能真正极其至,故魏椿所回答的是对的。然后朱子再问,一人知善恶,又一人真知善当为,恶不可为;此二人有何分别?按朱子所要求的答案应该是,真知者见善必为,见恶必去,即真知一定涵实践,另一人虽知善恶,但只是一般地知,不必能贯彻而为行动。而真知所以能有真正的道德实践,是知至一定意诚之故。[15]
5.孝述窃疑:心具众理,心虽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尝不在。但当其蔽隔之时,心自为心,理自为理,不相赘属。如“二”物未格(牟先生案:“二”当作“一”,下同),便觉此一物之理与“二”不“恨”入(二)当作
“心”,“恨”当作“相”),似为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无之(“邀”当作“邈”)。及既格之,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
未知而无,不以既知而有。然则所以若内若外者,岂其见之异耶?抑亦本无此事,而孝述所见之谬耶?先生批云:极是。[16]
此段李孝述所说的,朱子批云“极是”,应该便可以视作朱子的见解。此段认为理是心本有之物。只是心昏蔽时心与理不相赘属。格物之后,则觉得理是吾人素有之物,依牟先生,此段未能消解理在心外,“似从外去讨得来”之疑问;此处所说的心理的相属或心合理是在格物之后,即心通过后天的认知活动而关联到理。但其实亦可另做解释,此段强调理为心所固有,只是在昏蔽时心理不相属,一旦格之,心便知道理是本来固有的。这里一方面说心与理为二,另一方面说理固具于心,两种意思如何统一呢?我认为未必要如牟先生所说,心理是二,须由认知关联为一;可以用上文所说的由于理是道德之理,而此无条件的为其所当为之意义,是人的理性所首肯而不能反对的,故理虽不同于心,但心一旦明了此理,便会认为此理是吾心本来具有的。从自己对于此理的完全认同,便会觉得此理并不在心之外。朱子所说的心固然不是道德的本心,但对于道德之理是人心一反省就可以知道之义是屡屡言之的。
在《语类》有一条可以与上说相发明:
德元问:“何谓‘妙众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
理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所以谓之‘妙众理’,犹言能运用众理也。‘运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又问:
“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17](僩)
朱子所谓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可以从上文所说的当然之理来说,即人一旦了解此当然之理便会觉得此理是我本有的,非从外得。似乎只有从当然之理来了解朱子所谓的理,才能解消心理为二,但理又为心所本有二说之不一致。朱子于此段文说:“所谓知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即他反对心的知理是知心之外的道理之说,即朱子之意,心与理并不可用主客相对,理是心之外在的对象这一方式来了解。这也可以证上所说的一旦知道当然之理,从理所当然的体会中涵有“此理是我固有的”之肯定。故以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可以解消“心理为二”与“心本具理”二义之相冲突。此段又说,“知”是使本有之理发出来的作用。知不是理,此是当然的,但在知理时,此当然之理的意义,就在我心中显发出来。知此时便成为理的彰显,即由于有此知理之知的作用,让吾人明白了此为吾人所本具之当然之理。而且越知此“本具的当然之理”,越使吾人肯认此理,即认此理为“真实的存在”。
对于理是无条件的当然之理之义,可以从下列诸条见之:
问:“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曰:“只是见得天下事皆我所合当为而为之,非有所因而为之。然所谓天下之事皆我之所当为者,只恁地强信不得。须是学到那田地,经历磨炼多后,方信得过。”
问为己。曰:“这须要自看,逐日之间,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这便是无所为。且如读书,只道自家合当如此读,合当如此理会身己。才说要人知,便是有所为。如世上人才读书,便安排这个好做时文,此又为人之甚者。”
“‘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无所为,只是见得自家合当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钱谷、笾豆、有司,到当自家理会便理会,不是为别人了
理会。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其亲之病,一则是不忍其亲之死,这都是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器远问:“子房以家世相韩故,从少年结士,欲为韩报仇,这是有所为否?”曰:“他当初只一心欲为国报仇。只见这是个臣子合当做底事,不是为别人,不是要人知。”[18]
《语类》此三段都表明了“为己”,是“无所为而然”之义。为己是无所为而为,而为人便是有所为而为,此“有条件”“无条件”之辨,亦即是义利之辨。能明此义,方可说是知德,而且朱子此三段话都有“见得”之语,表示了对此无所为而然的道理,需要自己看出来。他对无所为而然,规定为“只是道我合当做便如此做”“不是要人道好”“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这些话都显示了朱子对于道德的行为是为了吾人所认为当如此行而行,如康德所说的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之义,有深切的了解。此可证朱子所说的理当该是道德之理,朱子对于道德行为只是行其所当然之义,有深切的体悟。对于此义,人虽都有了解,“但只恁地强信不得”,要进一步学、磨炼,方信得过。此即是要以格物致知进一步明了此当然的道德之理。
对于道德之理的体认也就是通过义利之辨而得到的理解,此对道德之理的理解不只是理解而已,在理解此理之同时便会生发出朝向此理而力求实践的愿望。于是,从对于道德之理的理解就会产生实践的力量。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了解到当然之理时,自己一定会肯定此理、赞成此理,而认为此理的规定是吾人本来就该如此做的。此理是我固有之理,既了解此理是我固有的,我所肯认的,那当然我就要把它实践出来。于是实践的力量就从明理、知理或朱子所说的“知极其至”而生发出来。于是致知的工夫虽然不能造成或达至知与理为一,但在知理的过程中,理的作用在吾人的生命中就得以彰显。道德之理如康德所说是理性的事实,此理性的事实一旦为吾人所了解,就不能不同意。而道德之理的力量就在此处生发出来。此如同上文朱子所说的“用知,方发得出来”之意。
在朱子与陈亮论汉唐的文字中,有以下一段:
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者,盖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莫能夺也,是岂才能血气所能哉![19]
此段说对于天理人欲之分,人不必在古今历史之王霸之迹上探究,只须反省吾心所认为义利、邪正之区分,便可了解。此即表示上文所说对于所谓道德之理,人反省便可知之之意。吾人之心对于义利、邪正之分是清楚的,而对义利之辨“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同于上文所说,对于道德之理之知是使理得到彰显之活动。而“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则也表示了对于道德之理的越加肯认便会越有力量,而自会朝此理的方向实践。此段说明了朱子说统中,知理可以诚意,或在对于理有所知时,理在人的生命中可以发生力量的根据。
四、结论
上文试图说明朱子意的致知格物所以能够达至诚意的论据,此论据的关键在于所知的理是当然之理、道德之理。而吾人对于道德之理一旦有所了解,便会加以肯认、赞同,而感到此理是吾人本有之理,是绝对不能反对的,反对之就等于反对自己的理性,也等于是自我否定。由于道德之理有如此的特性,故明白道德之理就使吾人不得不接受之,而愿意单因为是理的缘故便足以决定吾人的行为,如是就等于是道德之理产生了实践的力量。此道德之理的实践力量,依朱子是通过“知”才能产生的,故理虽然是我本有的,但必须要有知的作用,理的意义才能彰显。而知愈致,理的作用就愈得以生发。我认为如此解应可以为伊川、朱子强调“真知”及朱子意的“知至而后意诚”,做出较为顺当的解释。如果此说可通,则程朱对于道德之理的真知与阳明所说的致良知,都可以是儒家内圣之学的合理的工夫。除了上说之意外,按照康德所说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相涵蕴(互相回溯)之说[20],也可以说明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即对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越加了解,越会要求自己的意志需成为自由意志,即明道德之理会给出纯粹化自己的意志的动力。关于此意,我在另外的论文中已有阐述。[21]
当然,众所周知,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范围是很广的,他说一草一木乃至天地万物都有其理,照此说理当该不只是道德的当然之理。但朱子要穷的理虽多,最后是可以通到太极之理的。而太极之理只有一,故理之多,只是虚的多相,所谓“月印万川”。依上文分析,吾人有理由说此作为根源的一理或理之一,是道德的当然之理。又若从道德的当然之理来规定朱子所说的理,此理可以说是形式之理,只表示了一理所当然,当该无所为地去合做的事之意义,至于在人生的种种的关系、情境中,哪些作为是我们应该无条件的行所当为呢?这就需要加入对于人生种种情境、关系的考虑,而在这个层面上说理,则此理或这些理是有内容的,也需要去格,如对父母的孝顺是应无条件的,因为孝是该行而行的,但怎么样才是具体的孝行呢?则冬温夏凊等恰当的行为也需要研究,这些孝行或礼义便不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意义而已,这也需要去格。朱子所说的格物穷理,也常指这些意义的理或礼而言,但虽如此,此种种有内容的殊多之理,或礼仪,是在无条件地为所当为之形式之理规定下的,这好比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故此无条件的当然之理,是在先的。故我们还是有理由说,朱子所说的理主要是就此无所为而然的道德之理上说。(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
杨立华
关于理气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朱子哲学的核心。程颐用“所以”二字建立起形上、形下的严格界限,从而埋下了与理气关系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种子。当然,这些问题是到了朱子那里才真正得到充分展开的。
在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当中,理气动静问题最难索解。虽然此前的研究,对此也提出了一些看起来颇具说服力的说法,但其中仍有难以通贯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梳解。本文将“理生气”与“理气动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期对此问题的理解有所推进。
一、从程颐对张载的批评说起
《近思录》第一卷中有这样一段程子的话:
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将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1]正文后小注曰:“此段为横渠形溃反原之说而发也。”
《程氏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中有两段话,与此章相关:
若谓既返之气复将为方伸之气,必资于此,则殊与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气,以为造化?近取诸身,其开阖往来,见之鼻息,然不必须假吸复入以为呼。气则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至如海水,因阳盛而涸,及阴盛而生,亦不是将已涸之气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也。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天地中如洪炉,何物不销铄了?[2]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物销铄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3]
这几段论述都是在批评张载的虚气循环的气化宇宙论。在张载那里,太虚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这样一来,太虚之气也就成了由万物消散而来的气的某种形态,也就是程颐所说的“既斃之形,既返之气”。在程颐看来,万物一旦消散,也就灭尽无余了,不会回复到“太虚”这一气的原初状态,更不会成为新的创生过程的材料和基础。
程颐对张载的批评,朱子是完全认同的。《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有一则材料,与上引《近思录》中程子的话有直接的关联:
又问:“屈伸往来,只是理自如此。亦犹一阖一辟,阖固为辟之基,而辟亦为阖之基否?”曰:“气虽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气,自非既屈之气。气虽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谓‘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4]1这段话里,朱子充分肯定了程颐不能以“既返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的观点。其中,“物亦自一面生出”,强调的是创生的单向性,而不是像张载所讲的那样的循环。
上引《近思录》“近取诸身,百理皆具”一章下,江永集注中有这样一段解说:
果斋李氏曰:往而屈者,其气已散;来而伸者,其气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穷,若以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则是天地间只有许多气来来去去,造化之理不几于穷乎。释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轮回之说。[5]
这里提到的“果斋李氏”即朱子弟子李方子。李方子这段解说尤为透彻,也充分体现出了朱子对此一问题的看法。如果像张载所讲的那样,既散之气反归为太虚,太虚又聚而为气和万物,那么,宇宙间的气就有了恒定的量。所谓的造化不过是形态的改变,新的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了。
综上所述,程、朱对张载的虚气循环的思想的批评,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其一,虚气循环论等于肯定了气作为材料的永恒存在。而程、朱认为,气作为有具体规定的存在者,是有限的,终究会灭尽无余;其二,既然肯定了气或材料的永恒存在,理就只能是气的形式或结构,因此是附属于气的。这样一来,以理为根源的道德价值也就会失去它的根源性。程、朱当然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气是有成有毁的;其三,如果有永恒的气或材料,那么,天地造化就只是永恒材料在形态上的改变而已,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生生不已的创造。不再是生生不已,而只是永恒变化;其四,以永恒的气或材料为基础的造化,也就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依赖有恒定量的既有材料。这在程子和朱子那里,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二、理生气与理必“有”气既然消散的气
是灭尽无余的,也就意味着气的产生不是源自既有的材料,而完全“凭空”而来的。当然,讲气是凭空而来的,并不是道家意义上的无中生有。道家意义上的无中生有,是强调世界有其开端,万物产生之前,有一个绝对空无的阶段。朱子显然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无始无终的。在这没有开端和终结的世界里,具体的、有限的万物有始有终。具体的、有限的万物的产生,根源于凭空而来的有限的、分化的气。这实际上与郭象万物“自生”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6]与郭象不同的是,朱子认为气的产生根源于理。
在朱子那里,理是天地生生不已的根本。所以,“理生气”是很自然的一种理论的表达。朱子讲“理生气”,有两条材料。其一为《性理大全》中所引:“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此条材料经陈来先生考证,出自朱子弟子杨与立所编《朱子语略》。[7]另一条见于《朱子语类》:
谦之问:“天地之气,当其昏明驳杂之时,则其理亦随而昏明驳杂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气自如此。”又问:“若气如此,理不如此,则是理与气相离矣!”曰:“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
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8]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朱子讲到“气虽理之所生”时,并没有受到学生的质疑。由此可见,在当时日常讨论当中,这一表达并不令人惊异。至少,“理生气”的观念是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
但既然“理生气”的观念确是朱子的主张,且为门下弟子普遍接受,那么,为什么在现存的思想资料当中,“理生气”的明确表述却如此鲜见呢?可见,“理生气”或“气虽理之所生”这样的理论表述,并不是以理作为气的产生的根源的思想之准确表达。《语类》卷一有两条观念一致,但表述上略有区别的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是理后生是气,自“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此性自有仁义。[9]问理与气。曰:“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又问:“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未有人时,此理何在?”曰:“也只在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担,或取得一碗,都是这海水。
但是他为主,我为客;他较长久,我得之不久耳。”[10]
前一段材料中的“有是理后生是气”与后一段材料中的“有是理而后有是气”,表达的是相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朱子涉及理气关系的论述中,“生”和“有”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而朱子之所以很少讲“理生气”,则是因为“有是理便有是气”这样的表达更为准确。“理生气”其实只是“理必有气”的思想的一种较为随意的表达而已。
“理必有气”的观念充分体现在朱子关于仁义阴阳的论述当中。在朱子的哲学当中,仁义属理,本不应分阴阳,但朱子又明确有仁阳义阴的论述:
“仁礼属阳,属健;义智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是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11]
仁阳义阴的观念,绝非朱子一时之论。朱子晚年曾与袁枢就此问题论难往复。仁义虽是理,但有仁之理,便有仁之气,有义之理,便有义之气。仁义虽然属理,但已不像太极之理那样的无分别,而是分了段子的。仁作为理,自身便涵一种发舒伸展的倾向;义作为理,则有一种截断收敛的倾向。理必有其固有的“势”,而“势”就落入气的层面了。
理必有其固有倾向,也就是说,理必有气。天下没有不体现出某种气质性倾向的“孤露”之理。太极之理虽无分别,但既是“诚”之理,就体现出实的倾向来。只虚实的定向,已有了气质层面的趋向了。
既然理有其固有的倾向,这固有的倾向又必然有其气质层面的表现。理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就是气。太极是实有的生生之理。一切根源于太极生生之理的东西,有始必有终。始就是阳,就有动的意思;终就是阴,就有静的意思。动静互涵,阴中涵阳、阳中涵阴而成水、火。所以,天地间最初只有水、火二气: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12]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问:“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13]
由水、火二气,再凝结成天地万物。朱子的宇宙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理“有”动静
理气动静问题根源于周惇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有“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的表述。这一表述就自然引生了太极是否有动静的问题。在程颐以“所以”二字特别强调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之前,这个问题还并不构成真正的理论挑战。但在严格地区别了形上、形下,特别是理、气之后,理的动静问题就成了不能回避的哲学困境。在《太极图说解》中,朱子解释说: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14]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之有动静”这一表述。细读整段解说,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表述上的张力。单看“自其微者而观之,则沖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这样的论述,朱子似乎是在说,理当中有动静之理,而这动静之理是气的动静的根源。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动就有动之理,静就有静之理。由此出发,就难免落入柏拉图式的分有说的困境。朱子哲学既强调一本,不可能在根源处便如此支离。[15]
关于理的动静问题,朱子有很多不同的表述。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表述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但如能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中思想的一致性。《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有几则相关的材料:
问“动静者,所乘之机。”曰:“理搭于气而行。”
问“动静者,所乘之机。”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
周贵卿问“动静者,所乘之机”。曰:“机,是关捩子。踏著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16]
这几条材料讨论的都是《太极图说解》中的“动静者,所乘之机”这句话。其中,人乘马的比喻被广泛征引,用以说明朱子的理气动静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比喻。万物皆禀得太极之理,那么,太极之理是否会随万物的运动而运动呢?太极为形而上者,无形迹可言,因此无所谓动静。既然万物皆禀有太极,也可以说太极寓于动静之中。所以朱子说:“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这里,朱子对“机”的解释值得留意。“机,是关捩子”,指能转动的机械。“踏著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强调的是静以动为基,动以静为基,动静互为条件。因此,在解释《通书》中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时,朱子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17]
实际上,“太极之有动静”,其中的“有”字显然是经过了朱子深思熟虑的。《语类》卷九十四载:
梁文叔云:“太极兼动静而言。”曰:“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18]
这里,朱子特别强调不能说太极兼动静。不仅不能说太极兼动静,甚至也不能说太极贯穿在动静之中。
《语类》卷九十四里有一段对话,对太极贯动静的说法,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问:“动静,是太极动静?是阴阳动静?”曰:“是理动静。”问:“如此,则太极有模样?”曰:“无。”问:“南轩云‘太极之体至静’,如何?”
曰:“不是。”问:“又云‘所谓至静者,贯乎已发未发而言’,如何?”曰:“如此,则却成一不正当尖斜太极!”[19]
从表面上看,张栻的讲法与朱子所说静为太极之体、动为太极之用的思想并无二致。朱子之所以不能接受“至静者,贯乎已发未发”的说法,应该是因为如果至静之太极贯穿于动静之中,那也就等于在动静之外别立一太极,从而将太极与动静分隔开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太极有动静”这个讲法,是朱子关于理气动静问题的究竟说法。实际上,太极“有”动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理必“有”气,是相统一的。既然形而上之理,即使是无内在分别的太极,也有其固有的倾向,如太极就有个实的意思,仁就有个动和生的意思,义就有个静和杀的意思,那么,这种固有的倾向就必然体现出某种气质层面的表现。理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就是气。天下没有不具气质性倾向的理,无“孤露”之理。既然理必有气,气则在动静之中。所以,必然的结论就:理有动静。而这也就是朱子理气动静问题的最终结论。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无思有觉、圣凡体别
——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方旭东
前言
《中庸》首章末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提出了“中”“和”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又与“未发”和“发”连在一起,因此,后来宋代新儒家学者在讨论“中和”问题时,也将“未发”和“已发”作为一对独立的范畴加以分析,更由于朱子的加入,“中和”与“未发已发”问题上升为理学最热门的话头之一。在朱子那里,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未发已发”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它们分别指性与情,一是它们分别指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或阶段。[1]这两种含义分别指向理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关于未发工夫,不仅不同的理学家意见不一,乃至像朱子这样的学者,个人意见前后都有变化,使得这一问题十分复杂,也成为今人理解理学工夫论的一个难点。作为朝鲜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的李珥(栗谷,1536~1584),在阐述其儒学思想之时,亦涉及这一议题。了解栗谷对于未发工夫究竟持何观点,不仅对于把握栗谷思想的特质很有必要[2],对于弄清栗谷之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乃至朝鲜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异同,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本文以《圣学辑要》为中心考察栗谷的未发学说,盖栗谷著作虽丰,但与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则是《圣学辑要》一书。该书由五部分构成:统说第一,修己第二,正家第三,为政第四,圣贤道统第五。其中,修己部分最长,又被分成上、中、下三篇,凡十三章。从篇幅上看,“修己”无疑是《圣学辑要》的重点。栗谷为学是典型的程朱进路,伊川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3],栗谷拳拳服膺,“修己”篇的章节安排即充分体现了这一为学顺序:收敛章第三(敬之始)——穷理章第四——正心章第八(敬之终)。正心章详论涵养省察之意,该章前面说涵养,后面说省察。栗谷所说涵养,主要是指静时工夫,属未发范畴[4];而省察则主要是指动时工夫,属已发范畴。在涵养这个部分,栗谷主要选了程颐和朱熹语录,中间加了一段按语。正心章“涵养”一节的选文与按语,构成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栗谷所选诸家语录(包括按语所引),计有:程子(伊川)4条,朱子6条,真德秀(西山)1条,其学问门径及其对朱子的重视,一览无遗。栗谷所加按语,依其内容,可以分为4条:第1条论未发时无思虑而知觉不昧,第2条论未发时有无见闻,第3条论常人与圣贤未发之中之同异,第4条论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属未发工夫还是已发工夫。不难看出,这些按语都紧紧围绕未发问题展开,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尽在其中,而其关键则是未发时到底有无知觉。
1.未发之时,此心寂然,固无一毫思虑。但寂然之中,知觉不昧,有如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也。此处极难理会,但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据此可知,栗谷对于未发的理解包含两个要点:首先,未发时无思(毫无思虑);其次,未发时有觉(知觉不昧)。不难看出,这两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按照平常的理解,知觉与思虑很难分开。对于栗谷之说,很容易提出如下疑问:既然知觉不昧,也就是说,人有清醒的知觉,如何又能做到无一毫思虑?难道思虑不属于知觉?如果思虑不属于知觉,那么,栗谷所说的知觉又是指什么?
一、无思有觉
栗谷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要理解他所说的这两点,存在很大的困难,所谓“此处极难理会”。因此他建议,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敬守此心”即可。如果将栗谷此说与程颐答苏昞(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章做一对照,不难发现二者相似之处:
或曰:“先生(按:程颐)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一作最)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202页)
此节讨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究竟属动还是静,程颐先是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大概他自己也感到这个回答可能让人无可措手,遂告诉对方还是先去理会“敬”。栗谷在处理未发问题时,几乎照搬了伊川的教法。事实上,栗谷在选文中就收了伊川这一条材料。[5]
然而,在解释“敬以涵养”的具体方法(术)时,栗谷又回到未发的两个要点上来:“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看来,不弄清无思(思虑、念虑)有觉(知觉不昧、无少昏昧)的确切含义,也无法去做“敬以涵养”的工夫。
看下面这段话,栗谷所说的知觉似乎主要指见闻这类感觉。
2.或问:“未发时亦有见闻乎?”臣(按:栗谷自称)答曰:“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矣。若物之过乎目者,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过乎耳者,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虽有见闻,不作思惟,则不害其为未发也。故程子曰‘目须见,耳须闻’,朱子曰‘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以此观之,未发时亦有见闻矣。”(《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虽然问者没有直接就“未发时是否有知觉?”来请教,但“未发时是否有见闻?”这个问题与未发时思虑知觉的讨论显然相关。问者似乎困惑于“未发时亦有见闻”这样的说法,言下之意:有所见闻不就意味着已发吗?
栗谷了解问者心中之疑,所以一上来就说:在一般情况下,见物闻声往往会随之产生念虑,这当然属于已发状态。但他接着又指出,并不是所有闻见都一定会伴随着念虑,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物过乎目,人见之而已,不起见之之心;物过乎耳,人闻之而已,不起闻之之心,总之,虽有见闻,但人不作思惟。按照栗谷,这种情况应当被承认为未发。换句话说,不是有闻见就一定属于已发。在未发状态下,人一样可以有所闻见。这样,有无闻见这一点不应当被用来区分已发未发,有无思惟才是关键。那么,栗谷所说的“思惟”,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若见物闻声,念虑随发,则固属已发”这句话来看,“思惟”是指伴随所见所闻而起念。而从“不起见之之心”“不起闻之之心”这些话来看,“思惟”又似乎是指有目的或计划性的意识活动。如果说前者是起念于闻见之后,那么,后者就是起意于闻见之前。相应的,“不作思惟”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有所闻见,但在头脑(内心)没有激起任何联想、情感、欲求;另一种是没有打算闻见或没有任何闻见的冲动而被动地闻见。[6]
以上是分析的说法,在栗谷本人那里可能没有这样的自觉。对他而言,无论是起念还是着意,都代表着一种自我控制或决定的意向性活动,既不同于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反应,也不同于闻、见这样的主要与身(与心相对)相连的感觉或认知行为,后两种精神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不受自我控制或决定,俗语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有以形容之。
关于自我控制的意向性活动与情感反应和具身性认知活动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说明。通常,只要眼睛是睁着的,只要视力正常,当眼前出现一片樱花,人就会看到,得到感官方面的印象:好漂亮的樱花。这个行为不需要主体意志(will)参与其中,无关于意志或意向。春天看到樱花盛开,觉得赏心悦目,乃至流连忘返,这种情感反应也不是出于主体有意而为。但是,是留在书房里完成论文还是去公园赏花,这些行为则是由主体决断的。栗谷说的思惟,更多是主体决断的意志或意向活动。强调未发时有见闻,无非是想对闻见这类比较简单的感觉或知觉活动与思考、意欲这类相对复杂的理智、情感活动做出区分。就提出已发未发概念的《中庸》本文来说,未发主要是与喜怒哀乐等情感或情绪反应连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庸》并没有说“未发时感觉器官处于沉睡状态”,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作者,本来不会产生未发时有无见闻知觉这样的问题。那么,未发有无见闻知觉,是何时以及怎样变成了一个问题呢?历史地看,这是程颐、朱熹这些宋代理学家努力的结果。[7]事实上,栗谷这段话就提到了程、朱各一条语录。它再次显示,栗谷有关未发的看法是以程朱为旨归的。下面,我们就逐一参详。
2.1目须见,耳须闻。(程颐)
这句话出自伊川答苏季明问后章第11节[8],栗谷在选文中对原文做了具录:
(程子语录3)或曰:“当静坐时,物之过乎前者,还见不见?”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也。若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关于静坐时是否有见闻,伊川给了一个语境主义的回答:“看事如何”,有大事时(比如祭祀)无所见亦无所闻,而无事时则有所见亦有所闻。何以有此不同?伊川没有解释。此节与同章第3节可共看,后者亦是关于未发之前(当中之时)有无见闻的问答,其文如下:
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
如同之前有关动静的回答一样,伊川有关闻见的这个回答,亦有试图照顾两边的特点:一方面肯定目无见耳无闻,另一方面也提示见闻之理仍在。
将第3节与第11节对照,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按第3节,静时(当中之时)无见闻;按第11节,静时(无事时)有见闻。静时到底有无见闻?伊川的说法应以哪一个为准?又或者,伊川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朱子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耳有闻目有见。
如耳无闻目无见之答,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其误必矣。盖未发之时,但为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见,耳之有闻,则当愈益精明而不可乱,岂若心不在焉,而遂废耳目之用哉?(《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以下文前旒黈纩之说参之”,可见朱子是以第11节的说法为准,准确地说,是以第11节后半截“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为准。伊川关于“前旒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的说法在朱子看来是错误的。
但其(按伊川)曰“当祭祀时,无所见闻”,则古人之制祭服而设旒黈,虽曰欲其不得广视杂听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为真足以全蔽其聪明,使之一无见闻也。若曰履之有绚,以为行戒;尊之有禁,以为酒戒,然初未尝以是而遂不行不饮也。若使当祭之时,真为旒黈所塞,遂如聋瞽,则是礼容乐节,皆不能知,亦将何以致其诚意,而交于鬼神哉?程子之言,决不如是之过也。(《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按此分析,伊川答苏季明问的这条记录还存在失真问题。[9]总体上,朱子对伊川答苏季明之后章评价甚低:“程子备矣,但其答苏季明之后章,记录多失本真,答问不相对值”[10],“大抵此条最多谬误,盖听他人之问,而从旁窃记,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问者之情,是以致此乱道而误人耳。”(《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61~562页)[1]
朱子之所以坚持未发时亦有见闻,在哲学上,是基于他对两组概念所做的区分:心之知、耳之闻、目之见是一组,心之思、耳之听、目之视是一组。前者属未发,后者属已发。
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虽未发而未尝无;心之有思乃与耳之有听、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一有此则不得未发。故程子以有思为已发则可,而记者以无见无闻为未发则不可。若苦未信,则请更以程子之言证之。如称许渤为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尝有如此圣人?[12]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为非,此言皆何谓邪?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答吕子约第三十九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3页)
朱子对思、听、视的用法与一般无异,都是以之为动词,表示认识活动意。但朱子对知、闻、见的用法与一般则不同,一般是以之为认识的结果或内容,而朱子则以之为认识的能力。通常,人们会说:思而不知(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表示:真正的认识活动必须有意识(consciousness)参与其中,否则,就会出现没有结果的认识活动。朱子为了合于未发已发的规定,故于思、听、视不取活动义,而取能力义。实际上,准确表达朱子意思的词应该是:思考力、听力、视力,而不是:思、听、视。朱子所说的“有知觉”或“知觉不昧”,正是说认识能力或潜能,而不是说认识活动或认识结果。在未发的状态下,当然不能说有知、闻、见,但可以说有思考力、听力、视力。如果朱子只是强调未发状态下,心体的明觉不曾失去,这当然是不错的。就像以镜为喻:镜未照物,不妨其有光明(即能照之功),但不能说其中有影(所照之物影)。但是,当朱子说未发时有见有闻,在语义上就存在歧义,人们会以为是在说有所见有所闻(事实上,朱子本人有时就是这样用的,比如,他在上引这段话里就说“若必以未发时无所见闻”),这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如果没有有意识地去认识(思、听、视),何谈认识的结果或内容(知、闻、见)?而按伊川之见,有思即是已发[13,那么,有所见有所闻又如何还能说是未发呢?
这里的问题出在“思”上。由于伊川并没有规定“思”特指分散心神,使其不专一的“闲思杂虑”,人们当然可以将其广义地理解为所有的知觉活动。事实上,伊川本人有时也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伊川了解,他所说的“思”或“知觉”乃是特指产生使人从所从事的活动当中分散注意力的思虑、念头,再宣称“才思便是已发”或“才知觉便是已发”,就没有问题了。如此看来,未发已发成为问题,纠缠不清,是程朱(尤其是伊川)等人理解的问题,而非《中庸》本文的问题,因为,对《中庸》来说,它明明是讲喜怒哀乐之情的发动与否,而不是对所有知觉活动而言。[14]《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主要是指人心没有生出私心杂念,而并不是说心无知觉。
综观程、朱之说,无论是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还是关于未发时究竟属动还是静,其陈述都存在不能自洽和难以服人之处。栗谷采纳了经过朱子裁断的未发时亦有见闻之说,但从他在选取伊川论未发的语录时依然收入朱子批评甚烈的那条材料这一点来看,伊川之说的内在矛盾以及朱子对伊川的批评与修正,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二、圣凡体别
为驳斥以未有见闻为未发的观点,朱子更发展出一种未发之体上的圣凡区别说,其大意是:未发之时,普通人或有无见无闻之事,而圣人则决不如此,其心聪明洞彻,闻见不爽。栗谷注意到朱子的这个说法,在按语中做了引用。
2.2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朱熹)
此为朱子《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中语,栗谷所引不全,读者从中难知朱子“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之究竟,兹将上下文一并抄录。
须知上四句分别中和,不是说圣人事,只是泛说道理名色地头如此。下面说“致中和”,方是说做功夫处,而唯圣人为能尽之。若必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处,则只是一种神识昏昧底人,睡未足时被人惊觉,顷刻之间,不识四到时节,有此气象。圣贤之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决不如此。若必如此,则《洪范》五事当云“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乃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费尽工夫,却只养得成一枚痴呆罔两汉矣。
(《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35页)
朱子认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这个叙述才是“说做功夫处”,而且“唯圣人为能尽之”。至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只是解释“中”“和”等名词而已。朱子这样理解“致中和”,是把“致”看成动词,这个解释显然受到了《大学》“致知”一词的影响。而把“致中和”功夫看成只有圣人才能完成,则意味着,被子思认为是“天下之大本”的那个“中”,不是常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就能达到的,而只能是圣人才如此。朱子的这个说法在《中庸》本文当中也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如《中庸》第三十一章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第三十二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不过,朱子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却主要是《尚书·洪范》有关“五事”之说。
《尚书·洪范》提到九类常道(九畴),其中第二类就是所谓“五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指:貌、言、视、听、思。《洪范》作者还进一步规定了这五事所应达到的目标:“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汉]孔安国《尚书》卷七“洪范第六周书”,四部丛刊景宋本)从理论上说,恭、从、明、聪、睿这些性质是应然或规范,并不就是实然。不过,古人有一种倾向,即把这些规范看作主体内在自发的美德追求,孔子把这种自发的美德追求称之为“思”,而有所谓“九思”之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第十六》)[15]《礼记·玉藻》也有对君子容貌方面的要求,提出所谓“九容”之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礼记·玉藻第十三》)可以设想,一个君子经过长期修养,他在视听方面自然会达到聪、明之境,而其一举手一投足,也会给人以恭重之感。
从《洪范》本文看,貌、言、视、听、思这五事是各自独立的,但郑玄(127~200)在解释“睿作圣”时,认为“睿”是“通”的意思,还根据孔子说的“圣者,通也,兼四而明”把“圣”解释为“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16],从而,由“思”出发而达到的“圣”就变成了兼包貌、言、视、听四者的更高范畴。易言之,如果一个人通过“思”达到“圣”的境界,那么,他同时也就兼具了貌之恭、言之从、视之明、听之聪。合起来,就是:圣人聪明睿知。“聪明”是就耳目闻见这些感觉或知觉能力而言,本来并不是形容睿智(知)这样的理性能力,现在,经过学者诠释,《洪范》以及《中庸》当中包含了“圣人聪明睿知”这样的命题,就这样,原本形容感觉或知觉能力的聪明与形容理性能力的睿智很自然地结合到一起,并且,它们都统一在“圣”的名义之下。
对于这种聪明睿知的圣人,自然可以说其心“湛然渊静,聪明洞彻”,其听也聪,其视也明,亦即:即便与事物没有接触,其听之聪、视之明也不会消失。说未发时无见无闻,对于这样的圣人自然不适用。
伊川与苏季明讨论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的问题时,只是一概而论,还没有像朱子这样把常人与圣人分开来说。按照朱子,关于未发状态下有无见闻,准确的回答应该是:未发状态下,圣人有见有闻。至此,朱子实际上已对未发状态下“目须见,耳须闻”的说法做了一定的修正,相对于之前他就伊川答苏季明问所做的裁决——未发时,耳有闻目有见,现在这个说法在辞气上已经减弱很多。
关于未发时有无见闻,朱子观点的不同版本,都为栗谷所继承。如前所述,栗谷接受了“目须见耳须闻”之说,现在,他也赞成朱子的“圣人未发时有见有闻”论。
3.又问:“常人之心固有未发时矣,其中体亦与圣贤之未发无别耶?”臣(按:栗谷)答曰:“常人无涵养省察工夫,故其心不昏则乱,中体不立。幸于须臾之顷,不昏不乱,则其未发之中,亦与圣贤无别。但未久而或颓放,或胶扰,旋失其本体,则霎时之中,安能救终日之昏乱以立大本乎?”(《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12页)
在朱子那里,“圣人与常人,其未发之中体是否有别?”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以明晰的方式提出,朱子只是强调,《中庸》所说的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唯有圣人才能如此,至于常人未发之中是如何,朱子则语焉不详。[17]而在栗谷这里,问题已经被尖锐地摆到面前,令他无法回避。栗谷的回答,是“圣凡未发之体有别”说的一个较强版本。
依栗谷,没有做过涵养省察功夫的常人,其心不昏则乱,因此,其未发之中,与圣人(圣贤)有别。栗谷也提到,常人之心在某些时刻,也许不昏不乱,从而,其未发之中与圣贤无别,但这种时刻稍瞬即逝,总之,都难以担当《中庸》所说的“立天下之大本”的重任。
栗谷关于常人与圣人未发之同异的讨论,其核心涉及如何认识《中庸》所说的“中”。这个“中”,《中庸》既说它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又说它是“天下之大本”。就前一个说法而言,“中”是一个中性描述,只要符合“喜怒哀乐”未萌这个条件,任何人的心,这个时候都可以说是“中”。然而,就后一个说法而言,“中”就变成了价值源泉,从而,再不能说,任何人的心,都可以作为人类的价值源泉。合理的解释,只能像朱子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大本)的,是圣人未发之中。
吕大临(与叔)曾经把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理解为“未发之中”,结果被程颐讥为“不识大本”。伊川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认定赤子之心属已发,而《中庸》所说的“大本”是指“未发之中”。吕大临则为自己辩解说,孟子意义上的赤子之心正是指未发之际而言的,其特点是无所偏倚,完全符合“未发之中”的要求。[18]吕大临在申述时,也谈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同异的问题。
圣人智周万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岂非止取纯一无伪,可与圣人同乎?非谓无毫发之异也。(《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7页)
吕大临承认,赤子与圣人之心有所差异,但他坚持认为,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正是就其与圣人相同而言的。按照吕大临的理解,孟子所说的“纯一无伪”的赤子之心,是指其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易言之,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在其未发时无不同。
朱子在评论程颐答吕大临论中书时,一方面肯定了程颐关于赤子之心不是中而未远乎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对吕大临关于赤子之心属未发的说法也给予了一定的承认。
问:“赤子之心,指已发而言,然亦有未发时。”曰:“亦有未发时,但孟子所论,乃指其已发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无那赤子时
心。”(义刚)(《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问:“赤子之心,莫是发而未远乎中,不可作未发时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发时,也有已发时。今欲将赤子之心专作已发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但其已发未有私欲,故未远乎中耳。”(铢)(《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离娄下·大人者章”,第1341页)
与伊川一口断定赤子之心指已发的立场相比,朱子的看法显得更为圆融。而关于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之同异,朱子的观点与吕大临也更为接近,因为他说:“赤子之心,方其未发时,亦与老稚贤愚一同”。然而,如此一来,朱子关于“常人之心与圣人之心未发时之同异”的看法就显出其复杂的一面。
朱子这种“一同”论亦见于另一条材料。
……又问:“‘赤子之心’处,此是一篇大节目。程先生云:‘毫厘有异,得为大本乎?’看吕氏此处不特毫厘差,乃大段差。然毫厘差亦不得。圣
人之心如明镜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论圣人,与叔之失,却是认赤子之已发者皆为未发。”曰:“固是如此,然若论未发时,众人心亦不可与圣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天理别在一处去了。”曰:“如此说,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大抵此书答辞,亦有反为所窘处。当初不若只与论圣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则自分明。”(可学)(《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第2504页)
朱子不同意说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不同,可能主要是基于“性即理”的观念。[19]不过,朱子在对未发时众人之心与圣人相同做肯定陈述时,语气并不那么强烈,而是表现出某种审慎:“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亦有不扰扰时”。如果说众人或常人未发时心多扰扰,那当然不能说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同。按照这个表述,众人或常人之心未发时与圣人之心不同的概率要大于相同。栗谷关于圣人与常人未发之体有别还是无别的论述,在思路甚至个别用词上,都与朱子的这个表述有相似之处。有理由相信,栗谷之说是从朱子这里出去。
栗谷论未发的最后一条按语是关于李延平静中体认大本之说的评论。
4.又问:“延平先生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作何气象,朱子曰‘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此说何如?”臣(按:栗谷)答曰:“才有所
思,便是已发。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故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此不可不察。但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是亦一道也。”(《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2页)
“李先生静中体认大本”是朱子评其师李延平之教的话,语出《答何叔京第二书》: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答何叔京第二书》,《文集》卷四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此书写作年月,据陈来考证,当乾道二年丙戌(1166)。[20]时朱子37岁,即丙戌之悟“中和旧说”之际,上距延平之殁(隆兴元年癸未,1163)三载。
栗谷提到朱子晚年定论,以体认字为下得重,见《语类》卷一百三: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3~2604页)
按:朱子这里所说,只是自悔旧日[21]为李先生撰《行状》时下得语重,并没有点出“以体认字下得重”,盖《行状》原文为“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并无“体认”二字。“以体认字下得重”是栗谷自己的理解。包括前面所说的“既云体认,则是省察工夫,非未发时气象也”,其根据应当都是下面这条语录。
问:“延平欲于未发之前观其气象,此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
观时恁著意看,便也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不观观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4页)
朱子自述,对延平之教以伊川之语格之。这里提到的伊川语,还有栗谷所说的“才有所思,即是已发”,都是出自以下这条语录:
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页)
伊川正确地指出,“求中”之“求”含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计划性在里面,即是“思量”(思),而“既思,即是已发”。所以,“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旦存了求的念头,就不再处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状态,而变成已发状态了。对于延平之教,乃至整个龟山门下指诀,朱子的不满,不只是其在名义上说不通,更认为其有所偏。所谓偏,是指这种工夫过于偏向静而忽略了动。朱子认为,伊川的持敬之学相比之下就要中正平和得多。
……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
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596~2597页)
或问:近见廖子晦言,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
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却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第2602页)
问:伊川答苏季明云:“求中于喜怒哀乐,却是已发”。某观延平亦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为如何,此说又似与季明同。曰:但欲见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道,则流于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朱子语类》卷九十六,第2468页)
按照“既思即是已发”的观点,未发时做工夫几乎不可能,因为一有所念,就已经脱离未发状态。程、朱把体验、体认乃至观都理解为思量、思维,不能不说,这种解释太过偏于理性主义,道南一脉,尤其是延平,静中观未发气象,恰恰是以消除目的性或功利性念头(去念,融释)为特征的一种功夫。其日常修炼,以达到内心摆脱一切计较考虑的澄心为效验。
无疑,栗谷是程朱持敬之学的信奉者,以“观(体认、体验)未发时气象”为教法的延平乃至道南一脉的工夫论,与之终不相契,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栗谷对实践未发工夫的延平之教亦保有一份同情,要求“学者静坐时,作此工夫,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则于进学养心必有益”。然而,何谓“轻轻照顾未发时气象”,它与延平所说的“静中观未发气象”区别究竟何在?文献不足,不敢妄议。
结语
本文通过评述栗谷在《圣学辑要》“涵养”一节所加的按语,对栗谷有关未发的思想做了分析,具体揭示了他对程、朱之教尤其是朱子观点的继承。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处理对栗谷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富于争议的“四七”之辩的内容,尤其是栗谷有关人心道心或气质变化的思想对其未发之说的影响。囿于语言,笔者对韩国学界丰富的栗谷研究成果虽然很感兴趣却也无法吸收。因此,关于栗谷的未发思想,本文所做,应当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仅就笔者现有的考察来看,说栗谷之学是纯粹的朱子学路数,绝无可疑。栗谷作为一个朝鲜儒者,他对朱子学的熟稔程度,令身为中国学人的笔者感到吃惊,发自内心地表示敬佩。当然,笔者在肯定栗谷对程朱之学的认识与奉持的同时,也指出,栗谷对程朱理论的某些内部矛盾及其学说存在的病痛,似乎还缺乏明确的意识与进一步的讨论。总体上,就有关未发的思想来看,栗谷对朱子学,给笔者的印象是,继承有余,而开发不足。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朱人求
朱子的格物致知既是知识论又是工夫论,是为学的起点,也是为道的起点,是明明德的工夫,“全体大用”思想则是其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然而,何谓“吾心之全体大用”?学术界对此语焉不详。回到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发现,“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就是“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就是仁,就是性体情用,就是心之动静,就是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就是圣人气象等。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影响深远,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以及东亚儒学对此都有不同的诠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心之全体大用”
朱子之学问,如浩瀚的大海,漫无涯际,令人望而生畏。朱子之博大实不可一言以尽之。如果勉强做一概括,我想答案应该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1]。朱子十分明确地表示,“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修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2]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第一义,儒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道理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圣人创作《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所有人都能超凡入圣,一起进入圣人的境域,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格物”二字。四库馆臣也认为,“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3]
格物致知是为学的起点,是为道的起点,也是成圣的起点。何谓“格物”?何谓“致知”?朱子认为,《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于是仿照古人的意思写了一段“格物致知补传”,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的集中阐释,也是其晚年定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4]朱子认为,格就是到,物就是事。穷尽事物的道理,就要认识到极致即无所不到。致就是扩充、推广到极致,知就是识。扩充我的知识,就要做到知无不尽。这就是说,探求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奥秘,不可只停留在表面,要达到它的极处,即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只有持久努力,一旦豁然贯通,则事物的表里精粗、内心的全体大用都能彻底认知,获得一种彻悟性的知识,达到对最高天理的心领神会。这就叫作“物格”,叫作“知至”。“格物”之“物”,并非客观事物,“物犹事也”,尤指人伦物理,其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儒家价值的认同,格物致知乃在于确证内心固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寻找生命存在的社会意义与精神境界,以达到“全体大用”“心与理一”的最高觉悟和最高境界——道的境界、圣人境界。
概言之,朱子的格物致知的最后结果就是悟道,就是“豁然贯通”的悟的境界,具体所指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然而,这样一个彻悟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学术界多语焉不详。
格物致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工夫[5],悟道之后的境界分别对应两种境界,格物的结果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致知的结果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他们的最有利的证据似乎就是朱子回答剡伯问格物、致知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6]实质上,他们只看到第一句,而忽视了第二句。其实朱子格物致知的境界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是“合内外之道”的境界,既有外在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又有内在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二者的统一体。甚至,在朱子看来,“格物所以明此心。”[7]格物只要达到“里”的层面和“精”的层面,就开始达到“心”的全体大用的层面,就达到了“物格而后知至”的效果,“心”的全体大用才是格物的最终归宿。
那么,究竟什么是“表里精粗”呢?朱子认为,表里精粗首先指对“理”的认识的高低深浅。“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只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作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工夫,这唤作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8]“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晓其精,皆不可谓之格。”[9]朱子坚决反对只做表面工夫,不追求终极天理的学人。更反对那些仅仅追求内在真理,又嫌眼前道理粗浅,对事事物物都不理会的学人。理之“表里精粗”是一个整体,表与里、精与粗是天理的一体两面。如果认识达到“知得里,知得精”,二者就达到物格、知至的境地。
其次,表里指“人物之所共由”和“吾心之所独得”。“表者,人物之所共由;里者,吾心之所独得。表者,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
里者,乃是至隐至微,至亲至切,切要处。”[10]如果说,“表”是人物所共行之大道,是外在的,浅表的;那么,“里”就是我内心对大道的独特体认,它是非常隐秘、非常精微的,也是非常亲切可行的,是切中要害的。
再次,表里分别指“博我以文”和“约我以礼”。朱子回答弟子问表里时说:“所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是之谓表。至于‘约我以礼’,又要逼向身己上来,无一毫之不尽,是之谓里。”[11]所谓“博我以文”,就是要四面八方都见得通透无遗,这是从外面的广博而言;所谓“约我以礼”,就是要像自家身心去探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未尽之处,这是从内在的精深处立言。朱子弟子子升感慨地说,自古学问亦不过这两件事情。朱子肯定了子升的观点,更加强调一定要看得通透、彻底,才能到达“知至”的境地。
最后,精粗指认知与境界之高下。朱子在回答弟子问精粗时说:“如管仲之仁,亦谓之仁,此是粗处。至精处,则颜子三月之后或违之。又如‘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充无欲穿窬之心,则义不可胜用’。害人与穿窬固为不仁不义,此是粗底。然其实一念不当,则为不仁不义处。”[12]管仲之“仁”不过是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天下百姓得以保全,故孔子称颂他的仁德,这是指“事”而言,只不过是“仁”的外在表现。[13]而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这是指“心”而言,这才是“仁”的精妙、精微的境界。
在朱子看来,认识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就达到了“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究竟什么是体?什么是全体?究竟什么是用?什么是大用?“安卿问‘全体大用’。曰:‘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此身全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问:‘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如何是体?如何是用?’曰:‘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淳录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体。’”[14]体与用不即不离,体就是用,用就是体。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朱子所称许的“全体大用”呢?
首先,在一般的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5]。”“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6]“明德”即“心之本体”,人心具有万事万物的道理而能自然而然地接应万事万物。但人心受到气质之性的局限,被物欲所遮蔽,有时候不能发出本来固有的光明的德性,“明明德”就是要回到原初那一片光明的德性中去,回归本心原有的澄明。“人之明德,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汩于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云: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则又似必着意体察然后有见。”[17“明德”之“全体大用”具体体现在伦常日用之中,政事的具体运用只是“明德”的向外推衍而已。如果没有觉察到内心的光明的道德,人们就容易沉湎于物欲而不自知,无法恢复本心的自觉与自知。
其次,全体大用一开始指仁体义用。天命之性流行发用于伦常日用和万事万物之中,其全体就是“仁”,万事万物对天命之性的分享和发用,各安其性,各尽其分,这就是义。“熹尝谓天命之性流行,发用见于日用之间,无一息之不然,无一物之不体,其大端全体即所谓仁,而于其间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毫厘之间,不可差谬,即所谓义。立人之道不过二者,而二者则初未尝相离也,是以学者求仁精义,亦未尝不相为用。”[18]仁义是人道的核心价值,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决然分割为二。朱子反对否定精义的空言,认为这是告子“义外”说的错误的根源。如果不知“义”而空谈“仁”,则尽不到仁的全体大用的功用。
再次,在心的运动变化的层面,“全体大用”又指心之动静而言。“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体大用……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岁工夫,屏除旧习,案上只看六经语孟及程氏文字,着开扩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会,方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真实语。”[19]又说:“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此其所以能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也。圆神,方知变化二者阙一则用不妙,用不妙则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20]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动静不失其时,能开物成务,世界一片光明祥和,这就是本心的全体大用。
第四,“全体大用”又指“仁”。朱子认为,“德是逐件上理会底,仁是全体大用,当依靠处。”又说:“据德,是因事发见底;如因事父有孝,由事君有忠。依仁,是本体不可须臾离底。据德,如着衣吃饭;依仁,如鼻之呼吸气。僩”[21]针对蜚卿的提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朱子回答说:“‘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道夫”[22]仁是全体大用,它的发用就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
第五,在推行方式上,全体大用即是推己及人,就是孔子之忠恕之道,即“仁”的具体推衍。“故圣人举此心之全体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达者达人,以己及物,无些私意。如尧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以至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道理都拥出来。人杰”[23]心的向外推衍、发用,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推己及人。尧通过明明德的工夫而达到和睦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天人合一,就是推己及人,就是把儒家忠恕之道发挥到极致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明代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指出:“求终身之行于一言,可谓善学矣!其恕乎!言举斯心推诸彼而已矣!心体与天下相关,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学者苟随所在而扩充之,则全体大用无不由此出矣。非终身可行之道哉?”[24]
第六,在心性结构上,全体大用指性体情用。在心性结构上,朱子主张心、性、情三分,心主性情,心统性情。贺孙因举《大学或问》云:“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元有一贯意思。贺孙”[25]心是心的主宰,心之全体就是仁义礼智之性,心的发用,就是人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性即理,人性之中本来就具有众理,本来就能明万善,只是由于气质和物欲的杂质掺杂其中故昏暗不明。因而,只有剔尽心性的杂质,才能回归心性的光明,回归心性原初的光明的本体。“窃谓人性本具众理,本明万善,由气质物欲之杂,所以昏蔽。上智之资无此杂,故一明尽明,无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杂,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则去得一分之杂,直待所见尽明。所杂尽去,本性方复。学者体此,以致复性之功。”[26]
第七,“全体大用”指“圣人气象”。格物致知即到达圣贤之域。“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纵有敏钝迟速之不同,头势也都自向那边去了。”“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夔孙”[27]格物致知所达到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就是圣贤觉悟之后的境界,每个人一旦优入圣域,圣贤气象油然而生。“夫子之道如天,惟颜子得之夫子许多。大意思尽在颜子身上发见,如天地生物即在物上尽见,天地纯粹之气谓之发者,乃亦足以发之,发不必待颜子言之而后发也。颜子所以发圣人之蕴,恐不可以一事言。盖圣人全体大用,无不一一于颜子身上发见也。”[28]朱子称许的颜子气象就是“圣人气象”,体现出圣人的“全体大用”。这是一种自然和乐、从容、纯粹、澄明的气象,如天地生养万物,自然显现,生机盎然,在万事万物上自然体现。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朱子认为,颜子作为亚圣,其精纯度可得九分,但与孔子的十分和圆熟相比,在境界上还略逊一筹。
二、“心之全体”的具体发用
表面上,朱子格物致知只是追求“心之全体大用”的境界,其实,格物致知所追求的“全体大用”也包含“理”之“全体大用”。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心之全体大用”推至“理”之“全体大用”基本遵循的是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在逻辑,即从“德”到“治”的演变。后世许多思想家皆以“全体大用”为朱子理学的精神。[29]朱子充分肯定了弟子描述格物致知贯通之后的“心即理,理即心”的观点:“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先生所谓‘众理之精粗无不到’者,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吾心之光明照察无不周’者,全体大用无不明,随所诣而无不尽之谓……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30]这里的“心即理,理即心”与陆王心学不同,它指心与理不即不离,是格物致知的觉解境界,其实质就是“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意思。朱子强调,理必然有理之功用。“或问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31]朱子甚至声称,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个道理,外王之道与内圣之道也只是一个道理。所谓格物致知,也就是要知晓这个道理而已,这是《大学》一书的基本宗旨。“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颜回同道,岂必在位乃为为政哉!”[32]内圣外王之道,殊途同归,圣王与圣贤同道。大禹、后稷、颜回同道,并不是只有在位才能为政。
《大学》之道,内外一以贯之。“明德”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具众理而应万事”。明德的使命就在于唤醒内在生命的主体自觉,唤醒自己内在光明的德性,排除物欲的遮蔽,回到原初光明澄澈的本心。这个原本光明澄澈的内心包含着万理,自然能应接万物,因而,明明德既是明此心,也是明此理。内心明德的向外推衍,也就是从修身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明此明德,觉此明德,存此明德,不为物欲所遮蔽,只不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更大、任务更重而已。“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所以《大学》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学,则能知觉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学》一书,若理会得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33明明德需要从切近的身心由近及远推至家国天下,明明德的发用就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功效。“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见处理会,也且慢慢自见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识得!……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尧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尧一国之明德;‘黎民于变时雍’,是尧天下之明德。”[34]在朱子看来,明明德不仅要明此心,明此理,还包含着知此理、行此理的意义。“盖所谓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与我一把火,将此火照物,则无不烛。自家若灭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时,又是明其明德。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阙一。若阙一,则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35]光明的本心、透彻的道理就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把,既照亮了自己的内心,也照亮了他人和整个世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明明德”的工夫,包含着尽知和尽行两个方面。格物、致知就是要知得分明,知到极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要行得分明,行到极处,二者的结合才是朱子的“全体大用”。
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并穷尽事物的道理,它需要在具体事物上落实。格物就是就着具体事物而做穷理的工夫,因此朱子特别强调《大学》以格物的入手工夫就是在于要在事上理会,即事明理,真知力行,否则所认识的道理只是一个悬空的道理。朱子认为:“人多把这道理做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36]朱子格物致知工夫的真正落实,是“知之深”和“行之至”,即真知的获得和实践的圆满完成。致知所获得的“知”是“真知”,既是具有真切的感性经验之知,又是能真切实行的真知。二程指出,“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木。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37]真知就能力行,知而不行,只是认知太浅薄,没有达到致知的目的。在朱子看来,格物致知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夫,它还诉诸行动,致知之“知”是“真知”,即能实行的真正的知识,那些不能真正落实为行动的知识谈不上是“真知”。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只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它只知得五分,见识只识到那地位。譬诸穿窬,稍是个人,便不肯做,盖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伤事亦然。”[38]“‘反身而诚’,只是个真知。真实知得,则滔滔行将去,见得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39]只有圣贤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朱子认为,“反身而诚”便是真知。真的知得这个道理,气势磅礴地展开行动,直到见得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地,那种快乐才是无边无际的。朱子以格物致知建立理学,通过格物致知来贯通内在之理与外在之理,内心具备众多的理能自然应接万事万物,使得内外一体,心与理一,全体大用,知行一致。
“全体大用”的精神还必须在实践上予以落实,这也是“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子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有了“全体大用”的精神指引,朱子学在应接万事万物之中有所依仗。这一切不仅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充分体现在朱子书院教化、身心修炼、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理论与实践之中,它们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照亮了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与生活世界。
书院教育的推广。朱子是南宋书院教育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在南宋167所书院中,与朱子直接有关的书院有67所,占据40%以上,远远在同时代各位道学大师在之上,其对于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集中体现了朱子书院教化的理念。朱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40]《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作为为学的目标,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它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精神正是传统书院的首要精神。朱子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也就是实施道德教化,即用《尚书》标举的人伦教化于民众。它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道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朱子书院教化尤其重视“知行合一”,注重道德的践履。他接着说:“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41]笃行、修身、处事、接物,无不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笃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项认知的归宿,即把外在的求知转化为内在的生命,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在生命实践中展开落实。这样一来,书院之“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践履人伦则成为“为学”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即做到“穷理”和“笃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白鹿洞书院揭示》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学、问、思、辨,而把浓墨重彩涂抹在“修身”“处事”“接物”等“笃行”事务上,把知识的获得与身心修炼弥合得天衣无缝,这是典型的道学家的教化理念,足见朱子书院教化的经世关怀。[42]《白鹿洞书院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高度凝聚,影响久远,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历史上教育之金科玉律。
朱子家礼的实践。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也是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家礼》一书确实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朱子礼学建构与实践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其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和福建的民间婚礼基本遵从《朱子家礼》,郑志明先生还在台湾地区推广朱子丧礼,韩国和中国大陆对朱子祭礼都十分重视,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纪念日),韩国和中国大陆都会举行隆重的朱子祭礼仪式。与此关联的是以家族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的勃兴壮大,家谱文化、祠堂文化、宗亲论坛等日益兴盛,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些文化实践活动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它也有力地证明了朱子家礼茂盛的生命力。
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社仓制度,系南宋朱子首创的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孝宗乾道四年(1168),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情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43]淳熙八年(1181),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44]。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它也充分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视民如子、天下一家的淑世情怀。正是通过身心—家—国—天下的一体建构,朱子理学的精神关切也从自我扩充到家族、国家和整个世界。
三、朱子“全体大用”观的发展演变
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对朱子后学、陆王心学乃至东亚世界影响深远[4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朱子后学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承传与创新。对于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其晚年得意门生陈淳的理解十分到位并适当发挥。“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圣贤存养工夫至到,方其静而未发也,全体卓然,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这里。及其动而应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尔而未尝有丝毫铢两之差,而所谓鉴空衡平之体亦常自若而未尝与之俱往也。”[46]陈淳指出,心有体有用,“具众理”是体,“应万事”是用,心体寂然不动,这是指性之静而言,感而遂通是其发用,这是指情之动而言。圣贤存养工夫做得好,就能保持内心的贞定,其应接万事自然而然而没有丝毫的差错,这也是程颢、朱子极为推崇的“定性”的工夫和境界。朱子认为,定性就是明明德的工夫:“人心惟定则明。所谓定者,非是定于这里,全不修习,待他自明。惟是定后,却好去学。看来看去,久后自然彻。”[47]只有内心贞定,人心才能一片光明。朱子强调,定性之“定”,并非定在这里,完全不用修养工夫,而心之本体自然光明。[48]定性之后,一定要去学习、修炼,天长日久,自然就能看得透彻。应该肯定,陈淳的理解十分透彻十分系统,对朱子全体大用的四个层次区分得十分明晰。只是陈淳主要在解释“心”的观念,没有办法把“明德”“仁”及其发用、“圣贤气象”等内涵容纳进来。
朱子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的“全体大用”思想基本继承了朱子哲学的精神并有所创发,提出“明体达用”。真德秀认为,全体大用具体表现为“众理”与“万事”的体用关系,故全体大用又可以表达为:“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理即事,事即理”又指理与事(物)之间的体用关系,“体”指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用”指发为实践实行之事。真德秀认为:“大抵理之于事,元非二物。……惟圣贤之学,则以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二者相须,本无二致,此所以为无蔽也。”[49]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在事中,事在理中。真德秀进一步指出,学者求学无非就是穷理以致用,理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用途,功用必定有终极的原理,理就是用,用就是理。“独尝窃谓士之于学,穷理致用而已。理必达于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50]在这里,真德秀批判了佛老(异端)脱离事物空言道理,最后陷入空疏无用;而仅言事实而忽视大道,最终游于无根的粗浅之谈。只有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即用,用即理,二者融会贯通才能称之为学之成。但是怎样才能称为“学之成”呢?真德秀的解答十分精到——“成己成物”,这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为”主要就事功而言。古圣先贤的“为仁”“为邦”分别代表成己成物的极致,它期许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的实现,也即由内圣推至外王,完成王者的事功,建立王者的丰功伟绩,儒学的体用本末都集中体现在这里。
真西山之学,即“明体达用”之学。真德秀极力反对那种把儒家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学割裂为二的做法,他说:“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近世顾析而二焉。尚详世变者,指经术为迂;喜谈性命者,诋史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然则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为道之大全乎?故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天理不达诸事,其弊为无用。事不根诸理,其失为亡本。吾未见其可相离也。”[51]真德秀认为,儒家学问有经有史,性命道德之学是经,古今世变之学是史;同时前者又是个“理”,后者则是个“用”。换言之,“成己”是体,“成物”是用;内圣是体,外王是用。善学者应该本经参史、经史互证,这样才能“明理达用”,可见,真德秀努力在内圣和外王之间找到一个调和之处。蒙培元也认为,提倡“经史并用”、要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是真德秀学术的特色,这一点是对朱熹思想的一个发展。52后世多称道他的学说“有体有用”“明体达用”。清代张伯行说:“先生之学卓然有体有用,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也。”[53]清代雷也称:“先生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54]
真德秀还认为《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他运用朱子“全体大用”思想来推衍和阐释《大学》,著成《大学衍义》一书。朱子十分重视《大学》,他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55]又曰:“今且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56]可惜朱子未能完成这一设想,它的完成就是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真德秀指出:“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57]《大学衍义》一书的目的就是让人君明白尧舜禹的体用之学,由内在的修身养性而达之天下,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元代学者对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颇为平淡。元代大儒许谦认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全体即前具众理,大用即前应万事。”“表里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亲其道当孝,此是表;如《孝经》一书之中有许多节目,又诸书言孝节目不一,此是里。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谓其间事为礼节也。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谓事为礼节中之至理也。”[58]许谦对全体大用的理解没有太多的创新,但他对“表里精粗”有所推进,认为,粗是节目中之所当然,精是节目中之所以然,粗与精的关系于是巧妙地转化为事与理的关系。新安陈栎则基本沿袭了朱子对“全体大用”的理解,他指出,“久字与一旦字相应用力,积累多时,然后一朝脱然通透,吾心之全体即释明德章句所谓具众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谓应万事者也。”[59]元代朱子后学熊禾在他的《考亭书院记》一文中充分肯定朱子之学就是全体大用之学,表现出德与治、本与末的内在关联。“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60]朱子之学还继承了伏羲以来的道统,使得古圣先贤的全体大用之学重新大放光明。
明代邱浚对朱子的全体大用进行了系统的发挥和诠释,尤其重视其中的治道和致用。他认为,全体大用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朱子之学即圣门“全体大用”之学。“朱子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择焉而精,其在章句。语焉而详,其在或问乎。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其朱子自道欤。”“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下家传而人诵之,皆知圣门有全体大用之学,为学者不能外此以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则为伯道,用非其用,无体故也。学而外此则为异端,体非其体,无用故也。”[61]邱浚指出,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为学者不能离开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来追求圣贤之道,为治者不能离开《大学章句》《或问》来成就帝王之伟业。离开了朱子的《大学章句》《或问》,治道也就成了有用无体的霸道,治学则是有体无用的异端之学。
其次,《大学》为儒者全体大用之学。“《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62]“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经》,而撮其要于《大学》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于治平,举德义而措之于事,为酌古道而施之于今政,衍先儒之余义,补圣治之极功,惟知罄献芹之诚,罔暇顾续貂之诮。原夫一经十传,乃圣人全体大用之书,分为三纲八条,实学者修己治人之要。”[63]在邱浚看来,《大学》一书集中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是六经的浓缩精华版,不愧为儒家的全体大用之学的经典文本。邱浚尤其关注《大学》治国、平天下之方略,其《大学衍义补》集中衍义了《大学》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
第三,《易》者其体,《书》者其用。“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64]《易》乃群经之首,义理之宗,学者学习六经成为儒者,讲明义理并以此修身,这就是“全体”之学。其“大用”则表现为治人与为政,它也是学的完成。《书》经是古圣先贤为政的文献,最能体现政治的精神。
第四,“横渠四句”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表达。“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65圣人全体大用之学关乎道统的承传。“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66]从伏羲、尧、舜、禹、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这些圣人都在为有形而无心之天地立心,为有命而不能自遂之生民立命,使得凡夫俗子皆有机会优入圣域。而曾子的《大学》之教,则是为了承接孔子之精神和往圣之精神,接续道统,为万世开太平,承传圣人全体大用之学。横渠的“四句教”则是对《大学》全体大用思想的精练表达,是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集中体现。
最后,全体大用又指“圣德之全体大用”。“臣按:朱熹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67]“圣德之全体大用”指向的是内心至圣之德,它来源于上天“至诚之道”,唯有聪明圣知的圣人才能上达天德,才能完成“全体大用”的功效,实现“全体大用的境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尧舜这样的圣王,邱浚勉励帝王要有所作为,要向三代学习,向尧舜学习,上达天德,成为一代圣君。
四、几点思考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全体”就是心中包含所有的道理,所谓“大用”就是人心自然能应接万事万物。“全体大用”精神落实在实际的社会政治层面,就是朱子书院教化的实践、朱子社仓的建立以及《朱子家礼》的推广,而作为学术层面展开则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礼制研究,足见朱子思想中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致知与力行的统一。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承传与创新,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走向东亚世界,成为东亚思想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通过仔细梳理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
(一)隐藏在“全体大用”话语背后的信息十分丰富
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68](Barbara Johnstone,第102页)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全体大用”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透过朱子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朱子对内圣精神的推崇,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微言大义”的传统。具体而言,“全体大用”除了朱子《大学章句》所标榜的“明德”和“心具众理而应万事”,还有仁体义用、性体情用、心之动静、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圣人气象等不同的含义,这些内涵在“全体大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结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它们隐藏在结论的背后,被历史所遮蔽。从“仁体义用”到“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朱子哲学所经历的从片面到不断完善的艰辛历程。“全体大用”思想在朱子哲学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揭示,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朱子哲学的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只是朱子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只是其格物致知理论的一个环节。朱子的“格物”只是“明此心”,“全体大用”只是“心”之“全体大用”。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必须回到朱子哲学的心性语境中来定位。“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属于修身的功夫,它的向外发用可以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外在的功用只是心的作用的外推和放大,尽管朱子有诸多的社会关切,但在本质上它仍然属于心性儒学。因而,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社会功用也不宜过分放大,朱子的活动更多还是在书院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其社会事功总体来说建树不大,其在漳州任内正经界和晚年出任帝王师等活动则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也与他的内在于心性的“全体大用”思想紧密相关。
(二)“全体大用”思想所建构的社会语境
话语具有建构知识和社会的能力。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和沃戴克(R.Wodak)把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概括为: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权力关系是“话语的”(discursive),即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生和变化的场所;话语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69]后世对朱子的理解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全体大用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对它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的历史过程。在陈淳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仍然是一种真理权威,一种知识权力,只是在帮助他们完成心性知识的建构。师生知识共同体,朱子的思想与弟子的思想内部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真德秀那里,朱子的“全体大用”开始获得社会权力,走向权力的中心。元代朱子后学又走向了心性儒学的回归,明代邱浚则在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引导全体大用走向帝王之学。可见,后世对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经历了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的互动。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仓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后世对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解和演化也基本演绎着德与治、内圣与外王的思想进路。
(三)从“全体大用”的视角重新审视朱子的心与理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后世对其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朱子思想体系的理解。“全体大用”是格物的最后境界和归宿,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最高天理的认识。天理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心”与“理”是“一”还是“二”,二者的分野构成了理学与心学的分界线。牟宗三先生认为,“心具众理”是认知地具,及“既格”而现实地具之,此理固内在于心矣,然此“内在”是认知地摄之之内在,仍非孟子“仁义内在”之本体地固具之之内在。此种“内在”并不足以抵御“理外”之疑难。此仍是心理为二也。二即是外。[70](牟宗三,第368页)朱子思想的主旨为理学,理是根源性存在,是最高的实体。但并不表示此理只是心外之理,心与理截然为二。朱子虽然承认一物有一物之理,但他的格物就是“明此心”,“明此理”,是“明明德”的工夫。格物致知所到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心”不仅“具众理”,而且“包万理”,还能知“万理”。尽管朱子从本体论上坚决反对“心即理”,但“理”在心中,心具众理。心知众理,心管众理。所谓“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朱子语类》卷十八)一句话,在朱子的思想世界里,理为体,心为用,心包万理,心管万理,全体大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朱子指出,“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朱子语类》卷五)这种“心与理一”的境界,指心与理交相辉映,融为一体,随事而发,物来顺应,自然而然。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心学与理学对“心与理”的区分十分清晰,但在认识论和境界论意义上,“心与理一”是心学与理学家共同信守的基本理念和终极关怀。
(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哲学系)
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1]
——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
许家星
当朱子于“伪学”声中去世时,朱子学即身陷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在此情况下,以勉斋为首的朱门弟子以竭力弘扬朱子学为己任。在如何诠释朱子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弟子们虽因气质、学问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差异,但总体表现为以发明、维护朱子思想为宗旨。勉斋对朱子四书学的阐发,形成了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元诠释路向,奠定了诠释朱子四书学的基本样式,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勉斋学派,对“后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
勉斋认为,朱子最重要的著作是《四书集注》,但该书精密简严,且与《精义》《或问》《文集》《语类》颇多分歧之处,必须对之展开再阐释,方能把握其旨意所在。《论语通释》即是勉斋对朱子《论语》的诠释之作。据《勉斋年谱》可知,该书为勉斋一生心血所在,成于其生命之终。勉斋以《通释》命名此书,是希望消除朱子论说之分歧,以定于一是。门人对此书给予了高度推崇,认为已将朱子《论语》疏通无遗。陈宓《题叙通释》说:“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2]《通释》对《集注》本旨的发明,主要采用以下方式:揭示《集注》用语、用意、针砭,辨析两说异同,以达到羽翼朱子的目的。
(一)用语、用意、学弊。《集注》用语“浑然如经”,须对之加以拆解式讲解,方能使其意义显明,利于理解。勉斋对《论语》学而章注的“善”和“复初”曾做了如下阐发:“‘明善’谓明天下之理,‘复其初’则复其本然之善也。”[3]很多情况下勉斋直接就《集注》“字义”逐字做出解释,如逐一解释温良恭俭让章“过化存神”四字。
如果说“用语”的解释是说明朱子说了什么,那么“用意”则要进一步揭示“用语”后面的用心所在。勉斋常以“何也”“故曰”等作为引语表示此意,仍以“学而”章注文阐发为例:“言君子而复归于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何也?学而至于成德,又岂有他道哉。”[4]
勉斋尤为留意存在多种诠释可能的文字,如《集注》解“伯夷叔齐”章“怨是用希”为“人亦不甚怨之也”。勉斋认为“怨”的施事主体可以是己、亦可是人,指出《集注》“人怨”解依据的是伯夷叔齐的圣贤境界。
《集注》特别重视针砭学弊的诠释原则,勉斋亦秉承此点。如《集注》为了激发学者修道进德之心,对接舆、沮、溺、丈人给予了高度肯定。勉斋以激昂之辞对四子做了高度赞扬,表达了对贪慕荣利之徒的痛恨。在“吾岂匏瓜”章亦指出,匏瓜是蠢然无知觉之物,人是万物之灵,应有所贡献于世界。世人借夫子此说为谋食四方辩护,丧失进退之义,背离了圣人本旨,必须加以辨正。“世之奔走以糊其口于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况,失圣人之旨矣。”[5]
(二)两说异同。朱子四书学是以《集注》为核心的学术系统,但《集注》与《或问》《语类》等存在差异;《集注》所引二程学派之说与朱子思想存在差异;《集注》前后两解并存之异同值得留意;《集注》历经修改形成的前后差异之说,究竟何者为朱子定见,关乎朱子思想之把握。勉斋针对此四方面异同加以再诠释。
勉斋尤重视《集注》与《或问》的异同,《论孟集注》与《论孟或问》因写作时间、修改历程有别,彼此颇多差异。[6]勉斋对此多采取“两存之可也”的态度。如他指出见危致命章“《集注》以为‘庶乎其可’,则固恶其言之太快,然《或问》之意,则又与《集注》不同。读者两存之可也。”[7]《集注》认为“其可已矣”意在贬子张断语过于伤快,不够周全,但《或问》在比较“可也”与“其可已矣”时则认为前者贬抑,后者揄扬,《或问》说对学者仍有其价值,故当“两存之”。对《集注》与《语类》的不同,勉斋亦主张并存之。《集注》“三月不违”章注引“内外宾主之辨”说,《语类》对此有不同表述,勉斋从文义与义理双重角度给出两说并存的合理性。宾主说大概以屋子为喻,内主外宾,具体有两解:一是以仁为屋,心之出入往来为宾主。“其心三月不违仁”指心是否安于仁,更合乎文本义。二是以身为屋,仁之存亡为宾主,从文义言有所隔阂,但就义理言,此说心仁合一,心即是仁,心在即仁在,于为学工夫更紧切。
勉斋亦注意《或问》文义之误可能产生的义理偏差。如指出《或问》“切磋琢磨”的理解存在不当:
若谓“无谄无骄”为“如切如琢”,“乐与好礼”为“如磋如磨”,则下文“告往知来”一句便说不得。“切磋、琢磨”两句说得来也无精采……前之问答,盖言德之浅深;今之引《诗》,乃言学之疏密。[8]
《集注》指出切磋、琢磨是处理骨角、玉石的由粗到精的两项工序,切琢为粗,磋磨为精。勉斋认为,若将此粗精说直接对应于“无谄无骄”和“乐与好礼”,则会导致下文“告往知来”毫无着落,没有体现子贡的领悟与夫子的赞许,“切磋琢磨”说亦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和力量。此虽为微小文义差别,却不可放过。子贡师徒问答当与《诗》句讨论分开来看,分别指道德境界深浅和学问工夫疏密。
勉斋指出,《集注》引文与朱子注语总体应相互融洽、互为补足,“各有所发明也。”如“可与共学”章程、朱经权之说不同,勉斋认为,《集注》经权有别说使经、权意义分明而不至于混为一团;程子权变本质只是经说亦有道理,朱子所言对程子说具有补足、完善意义,“足以继此章之旨”。面对程、朱之异,包括勉斋在内的门人通常认为朱子解更好。如“祭如在”章,《集注》先引程子以孝敬释祭祀祖先神灵说,再补充己说。勉斋认为,祭祀根本在于真实无妄之诚意,朱子所补“诚意”恰补充了程子说之不足。勉斋有时直接指出程子说“不若《集注》之说为当”。如子夏之门人章的“先后”诠释,程子从教学次第立论,朱子就义理精粗而论,故朱子学更确。勉斋对朱子超越前人的推崇在关于仁的论述中表现得最鲜明,认为“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他在“仁而不佞”章说: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义,则仁之道无余蕴矣。……又断之曰“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深味“全体不息”四字,则学者而求至于仁,其至之标的,又昭然而可见矣。……其发前贤之未发而有功于后学,大矣![9]
朱子孝悌为仁之本章以心之德、爱之理六字阐发仁的名义,透彻周全,可谓穷其底蕴而无余,本章则以“全体不息”四字昭然标示求仁之方。此四字极其精密含蓄地阐发了仁道及行仁之方,远迈前贤而有功于学者。且“全体”二字已囊括《集注》后章所引延平“当理无私心”之说,“不息”又进一步揭示其言外之意。
勉斋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对程、朱异同并非一味是朱非程,而是以自身判断为准,对朱子说同样有不少批评,有时亦认为“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如关于学而章解,他在《复叶味道书》中说:
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则是君子然后不愠。以悦、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
程子之说,方为稳当。[10]
《集注》所引程子说认为只有做到不愠方才是君子,朱子本人则认为只有成德君子方能做到不愠。据本章悦、乐、不愠三句文本的内在语义关系,程子说更恰当。其实,朱子说和程子说显然互补,勉斋从中看出朱子之不妥,颇出乎意外。
朱子就《集注》前后两说并存的情况有明确解释,认为这是因两说皆有可取,无法舍弃,但前说要优于后说。勉斋据贴切文义和为学工夫的原则对之有所辨析。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忍”,《集注》有忍心、容忍前后两义,但所选范氏说为容忍义、谢氏说为忍心义,这样就使得本应在后的范氏容忍义反而在前。勉斋的解答是:范氏、谢氏论域不同,前者就全章而发,后者仅针对“是可忍”而论。又如人而不仁章《集注》先后引游酢、程子说。游氏以人心解仁,较程子以正理解仁更亲切。朱子同时选用二说,表明仁应当包含人心与正理的统一。在勉斋看来,心与仁的关系更为紧密。
《集注》初本与改本是朱子后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出朱子思想的演变,对准确把握朱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亦能考验学者对朱子思想的把握能力。勉斋指出“博学笃志”章存在初本和改本之别:前者“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过于分析,带有有所为而外求的弊病,后者“所存自熟”则纯从心之存主立论,专注于内心的操存涵养,进一步突出了心与仁的内在一体性,显示出《集注》修改之精密。
《集注》初本谓“心不外驰而事皆有益”,后乃以“所存自熟”易之。
盖初本以博笃切近为“心不外驰”,学志问思为“事皆有益”。其后易之者,则专主于“心之所存”而言也。……以此见《集注》愈改而愈精也。[11]
二、“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勉斋于朱子兼具女婿与弟子双重身份,深知朱子四书诠释用心之勤,故再三告诫学者对《集注》切不可抱轻易之心。出乎意料的是,勉斋在《论语》诠释中,对《集注》却不大客气地给予批评。《复叶味道书》集中表达了他对《集注》的修正看法:
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朱先生云:“敏于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此用《中庸》“有余不敢尽”之语,然所谓“慎”者,非以其有余而慎之也。“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事难行故当勉,言易肆故当慎耳。人而无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当用“其何以观”例。“志道、据德、依仁”不当作次第说,若作次第说,则“游艺”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据德、据德者未能依仁之病。……德则行道而有得于身,随其所得,守之而不失。[12
勉斋指出,不应为了保持统一而删除《语录》不同之说。朱子对二程语录的处理,亦是尽量保持原貌。天下义理无穷,并不能保证编者所见为的当之论。即便朱子穷毕生精力所注之《论语》,亦多有不满人意处,这恰可以借《语录》之说看出,《语录》异说具有参考、矫正《集注》的价值。他举出《集注》中四处错误,从文义、义理、工夫上加以批评:学而章朱子解不如程子说精当;以《中庸》“有余不敢尽”解释“慎于言”不妥,慎只是谨慎勉励,并无有余义;“何以行之”的“以”解为“能够”不对,当解为“居上不宽”章的“凭借”义;志道章《集注》《语录》皆反复言及四者先后次序不可乱、本末精粗必有序,这一视四者为造道次第的观点,不仅导致“游于艺”无所安置,且割裂了志道、据德、依仁与人的关联,学者对道、德、仁皆需要始终用力而不可有须臾放弃,四者在价值序列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它们是并列而非次第关系。在文义上,勉斋还质疑《集注》博文约礼章的“约,要也”说,认为此处约之于礼的“约”显然为动词,是“约之”义,训为“要”不合文理。如训为“约束”,虽合乎文义,却未能突出与“博”的对举义,当合二者而取之,为“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其实质不过是存心而已。勉斋有时会通过否定《集注》所引说来间接表达批评。如“君子九思”章《集注》引程子“九思各专其一”说,勉斋认为专一而思的弊病是泛泛而思却毫无统绪、效果,思应当建立在戒慎敬义的基础上。
历来对十五志学章的理解,存在一个困惑:夫子所言自十五有志至于七十不逾矩的修道历程当如何观之?是开示真实语还是示教象征语?《集注》引程子说,认为“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朱子自评为,“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认为夫子生知之圣,其进道修得次序未必循此阶梯而进,未必有如此明确的渐进过程。但圣人并不自以为是,其说乃为学者展示为学上升之次第,是夫子修道进程的大略标示,希望学者据此为准则而加以对照自勉,并非是夫子内心自以为已达到了圣人境界而托之以此谦虚推脱之辞。故此说虽为夫子的一种谦辞,但此谦辞仍有其真实内容所在。勉斋对此提出了批判性看法:
圣人生知安行,有见夫义理之在人,不啻如饥食渴饮之急,则夫知而必学,学而必好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十年十五年而后一进,亦圣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说者以为圣人立法谦辞以勉人,则圣人皆是架空虚诞之辞,岂圣人正大之心哉!故《集注》虽以勉人为辞而又以独觉其进为说,亦可见矣。[13]
所谓圣人生知安行乃是指知义理之深,学义理之笃,好义理之切,是对学的知之、好之、乐之,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本质所在。圣人与常人的区别不是从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成就论,而是就其对义理之学的学习态度、能力论。至于十年、十五年的进学层次,则是圣人之学达到某一层次自信的表现,是见之真、行之切的真实自得的流露,并非是圣人为了勉励学者、为学者立法的谦辞。《集注》尽管主张这是圣人之勉辞,但同时又提出是圣人“独觉其进”处。其实,《集注》更强调勉人、立法、谦虚之说,“独觉其进”说不过略有此意而已。勉斋则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以此作为对《集注》的批评修正。
朱子《集注》之修改完善,是在与弟子讲学辩难中展开的。朱子善于包容、吸取意见的学风培育了弟子勇于质疑的学术品格。勉斋尤其保持了这种学风,故对《集注》时加质疑,体现出唯理是从的精神,勇于批判亦成为勉斋学派的一大特色。如传勉斋学的江西一派,以“多不同于朱子”的饶双峰为代表,其对朱子四书义理有着精细辩难,涉及格物传、忠恕解、心性论等核心论题,如批评朱子忠恕之道说仅突出了忠恕的道体义而忽视了工夫义,犯了“主一而废一”的毛病;指出以朱子之高明、精密,对程子说的理解仍然存在重要差失,可见质疑问难之必要。“《集注》主一而废一,所以于曾子用工处,又别说从一路去。以老先生之高明精密,而于前人语意尤看得未尽如此。”[14]勉斋所传于浙江的北山学派亦秉承此种怀疑批判精神,如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从考据学入手,对《集注》文字音韵训诂等颇多补正。
三、“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
勉斋据当时学术情况,有意彰显了心的本体意义,提出“心便是性”“心便是仁”等心性为一思想,指出较之讲学穷理,“点检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之学才是工夫根本,是道之传承与否的关键所在,显示出对“心学”的包容与工夫论的内转。
“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勉斋体现出重“心”的立场,视心为万化根本,人身主宰,具有参赞天地之化育,修齐治平之效用,批评世人对心有所轻视。“心者,天地之蕴,化育之机……甚矣,人之轻视其心也。”[15]他于礼云章、人而不仁章辨别《集注》二说优劣时,皆强调心对于理的优先性,事理必须安顿在人心上才有意义,若无心为据依之地,则理是寡头无根的。并于《舜禹传心周程言性二图辨寄黄子洪》中提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的心性为一论,发朱子所未发。说:“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仁义礼智皆具于心,而谓‘心在性外’,可乎?至于为说,则曰‘心出于性’,何其与孟子之言相戾乎?……则此心之妙,但有虚明而无礼义矣。”[16]批评黄子洪的心在性外、心出于性说割裂了心性关系,作为性之内容的五常皆根于心,故性在心内,“心出于性”则导致心丧失了义理内涵,仅仅成为知觉虚明之心。在“明德”的讨论中他亦主张心即性、性即心的心性为一说。《复杨志仁书》说:
此但当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今观所答,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
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则仁又便是心。《大学》所解明德,则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17]
解答明德究竟是性是心的疑问,应从心性为一的角度着眼,批评杨志仁说导致心性为二。心与仁具有分合关系,既有各自为二,不可合一的情况,如颜子三月不违仁;亦有心即是仁的合一情况,如孟子仁人心说。“明德”则是心性即一的概念。勉斋特别突出了“心即仁也”这一心与仁相合的向度,在分析仁的内外宾主之辨即提出“以义理言,则心即仁也。……其旨尤切”。弟子双峰指出孟子“仁人心”与“求放心”之心皆应指义理之心,批评《集注》从知觉之心理解“求放心”,与“仁人心”说不相应。勉斋认同双峰说,提出心有义理、知觉两面,其中又存在专指一面和合指两面的情况,故心性之分合说需具体分析,“心字有专指知觉一边而言者,有专指义理一边而言者,有合知觉义理而为言者。须逐处看得分晓”。勉斋还提出“非性情之外别有心”说[18],意在强调心与性情并非为二,心就是性情,是性情中对之起主宰作用者。
勉斋指出,重章句与重存养的朱陆两家工夫主导学界,二者“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各有优劣。在一般意义上,勉斋主张讲学、存养不可偏废,此即朱子合尊德性、道问学为一的立场。《复饶伯舆》言,“守章句者不知存养之为切,谈存养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缓,各守一偏于先王之道,卒无得焉”[19]。但因药发病、矫正学弊是决定勉斋工夫立场的关键因素,有见于朱子学者易于偏向章句讲学,缺乏身心存养,勉斋反复呼吁学者工夫当从以讲学穷理为主转移到身心上来。存养决定了致知之效,无存养,致知将流入讲说文字的口耳之学而毫无益处,说“须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论辞章,恐终不济事也”[20]。
“检点身心”。勉斋反复论及学问根本就是治心修身。“学问之道,治心修身而已。”在给双峰信中指出,古人之学在身心用功,以检点身心为主,讲学穷理为辅。透过格物穷理与检点身心工夫的对比,突出检点身心工夫的主导地位。《复饶伯舆》言:
近亦颇觉古人为学,大抵先于身心上用功……无非欲人检点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故初学之法,且令格物穷理……亦卒归于检点身心而
已。年来学者,但见古人有格物穷理之说,但驰心于辨析讲论之间,而不务持养省察之实……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寻行数墨,入耳出口,以为即此便是学问,……则虽曰学者之众,而适足以为吾道之累也。[21]
就往古圣贤用功之语来看,如尧舜精一之传、文王心事之制等,皆是检点身心工夫。钻研圣贤经典的格物穷理之功,是为了探究为学之方、获得正确义理,以做到居敬集义,最终归于检点身心。检点身心是格物穷理的目标所在。为此,勉斋严厉斥责学者放荡身心,埋头义理辨析之中,丧失了操存涵养自我反省的身心工夫,流于言行背离的口耳之学,走向了圣人之教的背面。痛切指出,讲学穷理人数虽众,却不仅无益于道之传承,反而会伤害之。强调检点身心而非格物穷理,才是道之传承的根本所在。为此,他强调持养省察工夫与讲学穷理的区别,批评饶鲁将二者合说有误。
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曰吾惟讲学穷理者,皆务外者也。……居敬集义乃是要检点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晓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
可合而言之也。
既然圣贤教人工夫皆是检点身心,故学者为学用心,自当以持养省察、敬义夹持工夫为主,讲学穷理乃辅助涵养省察工夫者,为学不以持养省察为主,而仅仅追求讲学穷理,则是向外为人之学,而非切己向内之学。敬义工夫要求在念头思虑上用功,通过持养、省察双向并进之方,达到内直外方之效用。敬义是检点身心的实践工夫,格致是探究事理工夫,二者所主不同,应严格区分而不可混为一体。在与李燔的信中,他亦将检点身心与讲学穷理对立起来,痛斥流于讲学是儒道失传的罪魁祸首,强烈表达了应以身心点检为主的思想。《与李敬子司直书》言:
近读《中庸》,因推考古先圣贤言学,无非就身心上用工。……博文易而约礼难。后来学者专务其所易而常惮其所难,此道之所以无传……若
但务学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学问也。……独南康德契兄与诸贤维持,讲学最盛……但不知于身心上点检处如何耳。[22]
古代圣贤之学皆是就身心用工,如《书》之人心道心、《易》之直内方外,皆是论身心工夫而非讲学。夫子担心学者认识倾向一偏,故以博文与约礼对举,希望兼顾讲学之文与实践之礼。就先后论,博文在约礼之前;就难易论,约礼更甚于博文,而学者流于外在讲学而放弃了约礼工夫,直接导致道的失传。当以戒惧慎独工夫为补救之方,以之为毕生事业而时刻遵循,讲学穷理不过起讲明戒慎的辅助作用。如仅知讲学则丧失了学问根本,学问根本在于身心实践。南康虽然为目下师门讲学最盛之地,更应用功于身心检点。
勉斋反复指出检点身心的意义,以极为强烈的对比性措辞强调是否有检点工夫是人生分界所在。“不到此间议论,虽杀人放火,自不相干;既到此间议论,须是检点自己,从头到尾,得彻方是。”[23]晚年屡屡道及检点身心是人生唯一重要之事,百事皆当放下,唯独检点身心工夫不可丝毫放松。“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检点身心为急也。”[24]只有检点身心才能使人性光明、纯粹、洁净如初,而恢复本初,不负此生。“今亦他无所用心,只得检点身心,令明净纯洁,交还天地父母耳。”[25]
勉斋非常重视孟子的“求放心”说,认为此是极重要的身心工夫,提出“存心之学”与辞章记问之学的区别。人心受到物欲拖累,就会放荡奔跑,从而丧失天理之约束,故圣贤以战战兢兢的静存动察工夫,来确保本心的存在。孟子求放心说是对学者提出的真切警诫,事关儒家之道的传承,秦汉以来学者沉溺于辞章、记问之学而丧失了古人存心、求心之学,直到周程先生,方才接续道统。学者于动静寝食中,皆当时刻牢记“求放心”而不可须臾偏离之,此为读书穷理之根本。“且是以‘求放心’为本,一动一静、一寝一食,不可离此三字,便有以为之根本,然后可以读书玩理也。”[26]多次告诫学者读朱先生书,应加倍于求放心工夫,反复批评过于思索文义的行为。强调自家心灵是书本文义的主宰,不能以书本之说漫过身心,提出“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说,此与象山“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说精神颇有相通。并多方设法,诱导学者反归于求放心。
先生曰:“以心照书,无以书入心,可也。”又尝言,“学者役精神于文义而不反求诸心,终未免有口耳之学。”故于讲论之际,必宛转而归诸求放心、存天理者焉。[27]
勉斋亦强调存念头的重要。指出作为工夫之首的戒惧,具有自然、简易、内在、当下的特点,一念即是,不待他求,不待外索。直接将之简化为当下一念,这与心学的当下说相通。《复黄会卿》言,“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28]如能存心,则念头存而不失的当下,万理皆在。“存心则一念存,万理具”。帝王之学亦不过是通过检束、防制其心,使念头皆合乎中道。穷理玩索工夫未能专注精一,原因在于“反身一念”未能做到。而贤愚之分的关键亦在于为学念头是在身心之内还是在其之外。
勉斋尽管凸显了心的本体义,推崇反身向内的“求心”工夫,但并未走向象山“心学”,而是坚持并发展了朱子学的主敬立场。为学首要是检点身心而非读书,检点身心之首则是持敬。“为学须先理会心,理会心先须持敬。”[29]主敬不仅是求放心之要旨,更是必须牢记于心、须臾不可离的“护身符”,是学者为学的必备之方,是儒家抗拒一切鬼魔上身的救命符。“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便是护身符。”[30]
勉斋身心内转之学,得到后人的继承认可。吴昌裔指出,勉斋以居敬集义为主的身心点检向内工夫,是对文公之学的进一步推阐。“先生体贴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是则文公有功于程氏,而先生有助于师门。”[31]勉斋“内转”之学在弟子双峰那里得到弘扬。除批评朱子“求放心”章对“心”的理解析为义理与知觉外,在牛山之木章双峰又提出同样的批评。双峰之学体现出追求合一、简易之学的特点,多处批评朱子之解过于分析,如批评朱子将“诚”与“道”析为“本、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等说过于支离;以知行交互解三达德又“头绪未免太多”等。
朱陆异同是朱子后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北溪表现出极力捍卫师门、抨击象山的态度,勉斋对陆学态度相对温和,认为其最大问题是“不读书”,但勉斋自身对读书的态度又颇矛盾,认为只是第二义,第一义是持敬收心,批评“后生辈皆以为读书者,充塞时文之具矣”[32]。双峰虽亦不满于象山不读书说,却提出“尊德性以为之本”说。如何看待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判定朱陆学者立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双峰后学的吴澄则更因力倡“尊德性为本”而被视为陆学,成为元代朱陆合流的代表。其中虽不无误解,但自朱子格物穷理到勉斋“点检身心”再至双峰、草庐“尊德性为本”,确乎显示出“后朱子学”演变的某种真实轨迹和趋向。
勉斋《论语》诠释,体现出对朱子学羽翼、辨正、转向兼具的多重趋向,奠定了“后朱子学”经典诠释的基本样式,弘扬了朱子学的理性辨正精神,指引了朱子学转向内在身心的工夫路线,昭示了日后朱陆异同话题的彰显,对深入研究朱子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近思录专辑》简介
方笑一
众所周知,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是儒家自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宗师。作为其思想之承载,朱子著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朱子与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最受后世关注,被誉为“六经、四子之阶梯”“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在中国以至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历代学者或注解研习,或订补递修,创作过数量庞大的“后近思录”,这些文献是《近思录》学术史的载体,也是朱子学发展、传播史的一个缩影,在古籍版本、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各方面都具有巨大价值。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分设“《近思录》后续研究著述”子课题,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后近思录”凡二十一种,细致校勘,精心标点,是为《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近思录专辑》。
作为《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第一个专辑,交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思录专辑》,不惟内容精优,形制典丽,更将为《近思录》学术史专题研究提供最基本、可采信、成系列的文献资料库,对朱子后学思想、宋明理学乃至泛中华文化圈历史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近思录专辑》总目
第一册[宋]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
[宋]叶采近思录集解
南宋衢州学宫刻本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注解语录六百二十二条,是《近思录》注本中现存最早的宋刊本。半叶九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十七字,左右双栏,有界行,白口,顺鱼尾。杨伯嵒衍注时,拟定了十四卷卷名,注文多引用孔子、孟子、伊川、南轩、朱子、吕东莱等诸子之语要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注释,与历史上南宋叶采《集解》同中有异,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本次校点整理以北京大学藏本为底本。
南宋朱熹再传弟子叶采《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注解语录六百二十二条,成书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现存元刻本三种,或残缺或补修或抄配。明清时叶采《近思录集解》刻本繁多,盛行于世。本次校点整理以清初邵仁泓校刊本为底本,以元刻明修本为校本。叶采集解《近思录》时,根据各卷的主旨拟定了篇名,为后世《近思录》注释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纲领,叶采所拟篇目几乎成为一种范式,也成为后世续编、仿编者重要的参考纲目。叶氏注本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是历史上东亚学界非常尊崇的文本,影响久远。
第二册[宋]陈埴 近思杂问
[宋]蔡模 近思续录
[宋]蔡模 近思别录
[宋]佚名 近思后录
[明]江起鹏 近思录补
南宋朱熹再传弟子蔡模《近思续录》十四卷,是蔡模编纂朱熹语录四百三十八条而成,主要选自朱熹《文集》《语录》《易本义》《书传》《论语或问》《太极图》《论语集注》等。本次校点整理以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底本,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清柯崇朴校订,天盖楼藏版,嘉兴图书馆藏。以日本宽文八年(1668)刻本为校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该仿编本对后世东亚《近思录》续编、仿编者影响很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
南宋无名氏《近思别录》十四卷,据校点者考证认为是蔡模所为。蔡模此编采集朱子两挚友张栻与吕祖谦的语录共计一百零八条编纂而成。现存最早的藏本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宽文八年(1668)刻本《近思别录》,本次校点以此本为底本。它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第三册[清]张习孔 近思录传
[清]李文炤 近思录集解
《近思录传》十四卷,清张习孔撰。张习孔(1606~?),字念难,号黄岳,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于江都。父张正茂,善诗古文,有《元晨诗集》。习孔十一岁丧父,家道中落,无资求学,“然性好书,史、鉴、百家暨诗赋、稗野间有所觏”(《宗雅集叙》)。为诸生十年,于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官刑部郎中,九年(1652),官山东提学佥事,仅数月即丁母忧,“见世途崄巇,绝意仕进,家食十余年”(《家训》)。晚年侨居扬州,筑诒清堂。据本书自序,康熙十七年(1678)仍在世。习孔学术通博,贯于四部,著有《大易辨志》二十四卷,《檀弓问》四卷,《云谷卧余》二十卷、续八卷,《诒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另有《家训》一卷,《系辞字训》一卷,《七劝口号》一卷,《使蜀纪事》一卷。其中《云谷卧余》《诒清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据《近思录传》自序的落款可知,本书的最后编定时间为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然序中自述作者少时便受读《近思录》,“喜其约而备,微而显,昕夕玩诵,意有所会,辄不自揆,敬为传数行,附缀本文之下,以相发明,序次篇章悉本朱子之旧,日诠月徙,积成篇集”,可见本书的编纂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又据序中所云“自甲寅编定以来,又已数易其稿”,则初稿编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后又经修订,方成定稿。关于本书的编纂目的,作者在自序和凡说中皆有交代,一是不满于明人周公恕“取叶氏本参错离析之,先后倒乱,且有删逸”“创为二百余类,全失朱子之意”,欲恢复《近思录》一书的原貌,所谓“保其故物,无使紊轶”;二是作者也想将其长期阅读近思录的体悟记录下来,传之后世,所谓“微志窃同夫朱子”。故而,作者编纂本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无论我们对其内容做何评价,本书都是后世研究张习孔学术思想与近思录诠释史的一部重要文献。本书对《近思录》的诠释,主要着眼于义理的阐发,而非文字的训释,作者时常表露自己对于近思录所涉议题的种种看法,如云“善风俗,正人心者,全在上耳”(卷七《出处篇》),这是对当权者提出要求;又云:“国家之坏,由官邪也。今方能饰治而振起,则尊高洁之志,以励天下之廉耻,使不至于复坏。”(同上)这则是为治理腐败提供药方了。应当说,这些论述对后世颇有启迪。本书的版本,目前所知的仅有上海图书馆藏清诒清堂刻本十四卷,此本黑口,单鱼尾,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每卷首署作者名外,并署“男潮、渐同校”,为张习孔家刻本。末卷“殆亦与此意近”以下阙,故为残本。今以此本为底本加以校点整理,正文校以上海图书馆藏明吴邦模刻《近思录》白文本。由于本书为孤本,因此整理出版对于研究理学史和清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册[清]张伯行近 思录集解
《近思录集解》注家很多,此书注解颇遵叶采,偏于义理发微,且用语明白晓畅,疏解务于精细,令人难生歧义,一向受到清代理学家和各地学堂、书院学子的推崇,故有清一代,屡有刊刻,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伯行《近思录集解》的版本众多,学界多以乾隆元年(1736)尹会一重刻本最为嘉善,学者也多以此书为整理和研究对象,如张京华的《近思录集释》等书。但据各种著录,与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尚存天壤之间,最后几经周折,从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初刻本。经认真比对和研读,发现初刻本较尹会一重刻本多出40余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次整理,第一次以东京大学所藏初刻本为底本,校以尹会一重刻本和马氏存心堂刻本。因底本和校本的完备,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定本意义,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
第五册[清]张伯行 续近思录
[清]张伯行 广近思录
《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清张伯行辑。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学者称“仪封先生”。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后入值南书房,由户部侍郎擢礼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卒于官,赐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张伯行学宗程朱,笃信谨守,躬行实践,居官清廉刚直,清圣祖称誉为“天下清官第一”,世宗曾钦赐“礼乐名臣”四字褒之。
自《近思录》编订行世以来,由于其作为理学经典文本和入德之门的重要地位,备受后世儒者的推崇和重视,历代注解诠释之作层出不穷,而依仿续编之作亦蔚为大观,张伯行所辑《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即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张氏于《近思录》极为服膺,以为其书“体用兼该,义理条贯”,学者由此问途,方可望见先圣门墙,进而深入堂奥,故对其详加诠释疏解,撰成《近思录集解》,后又相继纂成《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十四卷,凡六百三十九条,皆采辑朱子之语,并为之疏解。《广近思录》十四卷,凡一千二百十七条,每卷依次采择宋张栻、吕祖谦、黄榦,元许衡,明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七家之言。二书分卷门目仿诸《近思录》之例,所采录条目皆依据“关于大体,切于日用”之标准。据张氏自言:“余于《近思录》所为既诠释之而又续之,既续之而又广之,冀有以章明义蕴,引进后人,而且以辅翼儒书于不堕也”,“学者诚由《近思录》而并及夫《续》与《广》二录,寻绎玩味,沉潜反复,万殊一理,悠然会心,然后六经四子之书不为日耳,当必有身体而心验之者,入圣之阶梯无逾斯矣”。是为其所以纂集此二书之意。从《近思录集解》到《续近思录》《广近思录》,构成一个脉络相承的经典体系,体现了张伯行对程朱理学渊源统绪和论学要旨的认识、提炼和阐扬,对《近思录》的流传和理学的发展皆有积极意义。
《续近思录》《广近思录》今存刻本两种,分别为康熙年间苏州正谊堂刻本(康熙初刻本)和同治年间福州正谊堂全书本(同治重刊本),其中康熙初刻本较为稀见,而同治重刊本流传较广。但同治重刊本其所据之原本内容已有残缺,且校勘不甚精审,故其版本价值远不及康熙初刻本。此次校点整理,我们利用康熙初刻本作为底本,以同治重刊本作为校本,同时广泛参校所引诸家之书,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认真进行文字校勘,准确施加标点符号,精心撰写校勘记,力求形成精审准确的现代通行本,从而为广大读者带来方便。这也是此二书首次系统整理出版,因此该整理本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具有极大出版价值。
第六册[清]黄叔璥 近思录集朱
清代黄叔璥《近思录集朱》十四卷,稿本,现仅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成书于1754年,作者将散见于《或问》《语类》《大全》《文集》内的朱子言论,裒辑荟萃,附于《近思录》正文下。此外,还汇集了先贤,朱子的好友、门人、后学等著述中可发明《近思录》的言语,堪称续、广《近思录》诸书中“以朱释朱”一巅峰之作。此书因为是未竟稿,堪称稿本信息著录之集大成者,是从事版本、校勘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可不研读的精品。目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子海珍本编》据国图所藏稿本影印收录此书。迄今为止,还未见有关此书的校点整理本问世。整理出版此书,应该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第七册[清]茅星来 近思录集注
朱熹《近思录》是一部指导初学入门的理学启蒙书。《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是对《近思录》的详细注释,清茅星来撰。茅星来(1678~1748)字岂宿,浙江归安人。他极其推崇朱子的学说,因对于当时坊间流行的叶采、杨伯嵒《近思录》注释不满意,“病其粗率肤浅,解所不必解,而稍费拟议者则阙,又多彼此错乱,字句讹舛”。故此,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有以下特点:一:博采众说,参以己见。“取四先生全书及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二:名物训诂,考证尤详。“其名物训诂,虽非是书所重,亦必详其本末。”后人以为,开清人以考据方式注解《近思录》之风尚,并为乾嘉时期江永的集注《近思录》导乎先路者,即茅星来。其《近思录集注》亦为清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之一。
第八册[清]施璜 五子近思录发明
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是朱熹、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的一个重要衍生品。《四库提要》介绍朱熹、吕祖谦合辑的《近思录》云:
臣等谨案:《近思录》十四卷,宋朱子与吕祖谦所共辑。盖周、张、二程之书,宏深奥衍,承学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虑其不知所择,因与祖谦分类辑纂,以成是书。书以“近思”名,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论者谓为《五经》之阶梯,信不诬欤!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后因有续而广之者,亦堪辅翼,而权舆之精,无过是编云。
由此可知,在朱、吕合辑的《近思录》中只有四子,没有朱熹。《近思录》由四子变为五子,肇始于清初的汪佑。汪佑也是休宁人,学者称为星溪先生。施璜在《五子近思录发明序》中记此事云:
(朱子)尝谓学者曰:“《四书》者,《五经》之阶梯;《近思录》者,《四书》之阶梯。”夫阶梯也者,言所由以从入之序也。然则《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则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则不可以言《四书》也明矣。虽然,孔子之道自孟子后失传者一千四百余年,至周子、二程子、张子而始着,至朱子而始大着。夫既集周、程、张四先生之言为阶梯,若不得朱子精粹切要之言合观之,则学者终有所缺憾。故星溪汪子(按:即汪佑)将琼山先生所著《朱子学的》,与梁溪先生所著《朱子节要》合编之,以续于周、程、张之后,《近思》于是为完书,而阶梯之说亦于是为详备矣。
实事求是地说,汪佑《五子近思录》超过了朱、吕合辑的《近思录》。为什么?因为讲宋明理学而没有朱熹,缺了主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从数量上来说,朱、吕合辑的《近思录》原共六百二十二条,汪佑分门别类予以增补,共增补朱子语录五百四十八条,合计一千一百七十条。
朱、吕合辑的《近思录》,注者多家。而汪佑《五子近思录》尚未有注家。施璜是《五子近思录》唯一的注家。施璜的注释不叫注释,而叫“发明”。之所以叫“发明”,是因为施璜的注释主要是采用明代理学家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四家著作中的原话来发明五子的真谛,故曰“发明”。这样的注释方法,近乎清人所说的“以经解经”,说服力更强。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说:“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由此可知《五子近思录》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所占的地位。而要透彻理解《五子近思录》的内容,则《五子近思录发明》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此书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精华,其注释水平亦非今日之今注今译所能遽然企及。考虑到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中所占的地位,为了满足研究宋明理学的需要,则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的出版价值不言而喻。
第九册[清]江永 近思录集注
[清]汪绂 读近思录
《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清江永撰。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号慎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康熙四十年(1701)岁试,补婺源学弟子员;雍正八年(1730)檄升太学,因家计艰难而未赴;乾隆十五年(1750)特诏荐举经明行修之士,婺源县令特往起之,称病且老而谢之;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终年八十有二。江永邃于经学,尤精三礼,兼擅音韵、钟律、步算之学。不止发挥汉学,精擅考据,且能深入宋儒奥窔,研悦而羽翼之,卓然为当世大儒。
《近思录集注》的特点:一是仍《朱子遗书》原本《近思录》次第,恢复旧貌;二是“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集注》既出传世,即为编修四库全书收入,馆臣称其“引据颇为详洽”,“亦具有体例,与空谈尊朱者异也”。儒林学界,并多赞誉,谓之“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至为精切”,“比类发明,条理精密,不特不敢轻下己见,并不敢杂以他儒之议论,俾后之学者一意遵朱而不惑于多歧”云云,以为“自叶仲圭集解以下注释者数家,惟此最为善本”。是以,后世屡屡重刻再造,成为清中期以降最为流行的近思录注本。
第十册[清]刘源渌 近思续录
钱穆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宋代理学三书随札》)正是由于《近思录》这种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后世出现了不少与其相关的书。其中清初理学家刘源渌的《近思续录》,便是颇有特色的一部著作。此书因朱熹《近思录》篇目,采辑朱熹《文集》《语类》《或问》精粹分门编辑,分内外两篇,以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为修己之本,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异端、圣贤为治人之事。据刘源渌门人陈舜锡、马恒谦所作序,为编此书,刘源渌沥尽心血二十余年,意在以此书为《近思录》之阶梯。
第十一册[清]陈沆 近思录补注
[清]郭嵩焘 近思录注
[清]吕永辉 国朝近思录
《近思录补注》十四卷,清陈沆撰。陈沆(1785~1825),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年四十一卒。陈沆以诗文饮誉当时,《近思录补注》是其唯一的学术著作。
自《近思录》问世以来,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其中以江永《近思录集注》最为著名。《近思录补注》则基于江永《近思录集注》而作,全书对江永《集注》多有因袭取舍。其注解之特色,是略于训诂考证,亦不重诠解文义,而重在采辑后儒之说,借以阐明本文旨意。注文所引以朱子之说为主,与江永《集注》性质相似,具有“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特点。此外还广泛采择自宋至清诸儒之说,间亦附有陈氏本人的案断发明。
《近思录补注》是比较重要的《近思录》注本,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相较而言,江永《近思录集注》很多条目的注解比较简略,有些甚至没有注文,而《近思录补注》则广征博引,荟萃众说,补入大量注文,注解更为详密。作为晚出之《近思录》注本,《近思录补注》充分汇集前人成果,对叶采《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等,亦皆有借鉴参考,而其所引据诸儒论说,总数不下七八十家,其中不乏具有重要价值者。如所引魏源之说十一条,魏源文集中均不见记载,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又引秦氏别隐之说三十八条,其姓氏著作皆隐而不彰,录存秘逸,洵属可贵。《近思录补注》之价值意义,即此可见一斑。
《近思录补注》今存钞本一种,系陈氏原稿,现藏湖北省图书馆,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刻本有多部,藏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等处。迄今为止,《近思录补注》尚未经校点整理,对其流传和研究是重大缺憾。因稿本多有增删修改和墨笔勾画之迹,很多字迹难以识别,而刻本数部庋藏于图书馆,流传亦不甚广,对普通读者而言实不便于阅读。此次校点整理,我们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精心选择底本和校本,认真进行标点和文字校勘,力求提供一部精审准确的现代通行本,从而为读者带来方便。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周惇颐墓
——其历史与现状
〔日〕吾妻重二 傅锡洪译
前言
北宋的周惇颐(1017~1073)是近世东亚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他的揭示宇宙生成与构造的《太极图·图说》,不拘泥于俗务的“胸中洒落”的高雅精神,以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圣的“圣人可学论”等等,都无不因其蕴含深刻的思想和崭新的内容,而被南宋的朱熹(1130~1200)吸收从而构成朱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周惇颐的思想与品格对其后的中国以及韩国、越南、日本等所谓“儒教文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笔者在旧作中已有论及。[1]
笔者于2011年10月19日至20日参加了一次国际朱子会议并发表了论文[2],这次会议是在与朱熹渊源极深的,位于江西庐山山麓的白鹿洞书院召开的。会议结束后的10月21日,笔者得以拜访了周惇颐墓。[3]
周惇颐的墓位于庐山北部的九江市南郊。在历尽沧桑之后,如今已经整修得气势恢宏。本文即欲对其曲折的历史以及现状进行考察。它近来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情况。
另外还须交代的是,本文使用的周惇颐文集是十二卷的南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的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八八,书目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南宋版《文集》”。
一、周惇颐墓
周惇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天禧元年(1017)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他因恩荫入仕,但始终与权力中枢无缘,而是作为地方行政官迁转于江西、湖南、四川和广东等地,并取得政绩。这期间,在南安军(今江西南部)他教授了少年时代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熙宁四年(1071)八月初,已经五十五岁,步入迟暮之年的周惇颐出任位于庐山东面的南康军的知事,但他随即隐退,住进建于庐山北部莲花峰山麓的“濂溪书堂”,并在那里度过了晚年。熙宁六年(1073),周惇颐去世,享年五十七岁。[4]
周惇颐的墓建于“江州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的三起山。[5]如后所述,这个墓区是由清末光绪年间所扩大和整修而来,清代当时的地名是“九江郡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栗树岭”(栗树岭即三起山),位于庐山莲花峰以北20里,即现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周家湾。
饶有趣味的是,埋葬于此的除了周惇颐以外,还有他的母亲郑氏、他的原配陆氏以及继室蒲氏,为四人的合葬墓。接下来本文就考察他们四人先后埋葬于此的经过。
1.母亲郑氏(仙居县太君)。周惇颐的母亲郑氏是郑璨的女儿,郑向的妹妹,她嫁给了周惇颐的父亲周辅成。周辅成是特奏名赐进士出身,天圣九年(1031)卒于贺州桂岭(今广东北部)令任上,葬于家乡道州营道县。十五岁便成为孤儿的周惇颐,跟随母亲寄身于舅舅郑向门下。郑向是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任过知制诰,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成为杭州知事的高官,周惇颐入仕也是受其恩荫。不过在周惇颐母子投靠五年之后的景祐三年(1036),郑向便在知杭州的任上去世,死后葬于润州丹徒县(今江苏镇江)。接着,次年景祐四年(1037)七月郑氏于五十五岁之际去世,死后葬于郑向的墓旁。
然而后来润州的墓因为水害而损毁,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十六日,刚刚就任南康军知事的周惇颐特意将母亲郑氏的遗骸移至庐山,将其改葬于现在的墓地。潘兴嗣在《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南宋版《文集》卷八)中详细记载了此事。
此外,关于母亲郑氏的改葬,度正在其《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南宋版《文集》卷首,以下简称《年表》)的“熙宁四年”条目中有如下的记载:
俄得疾,闻水啮仙居县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军。十二月十六日改葬于江州德化县清泉社三起山。葬毕曰:“强疾而来者,为
葬耳。今犹欲以病污麾绂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
另外潘兴嗣的《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在叙述郑氏葬于润州之后接着记载道:
后二十年,水坏墓道。惇颐以虞部郎中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乞知南康军。遂迁夫人之衬窆于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也。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周惇颐乞知南康军不外乎是为了将母亲改葬到庐山。尤其是《年表》中所说“强疾而来者,为葬耳”,可以让我们强烈意识到这一点。
而《仙居县太君墓志铭》的说法则略有不同,患病、乞知南康和改葬母亲这一连串的事情具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年表》最后“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说的是周惇颐辞去南康军的职务,转而担任南京应天府的分司官。分司官即便不担任实际职务也可获得一定俸禄,乃是官员将要引退之际担任的闲职官。[6]这也意味着周惇颐就任南康军仅仅四月有余。由此可推知,患病后的周惇颐考虑在自己所酷爱的庐山隐居下来[7],安静地度过余生,并希望将母亲的墓安置在其旁边。母亲郑氏在丈夫去世之后艰难地将周惇颐抚养成人则已如前所述。
而郑氏在去世后获赠“仙居县太君”的称号,依照的则是北宋当时对文武百官的母亲以及妻子实行的叙封制度。[8]
2.妻子陆氏(缙云县君)。正室陆氏是职方郎中陆参的女儿,在景祐三年(1036)周惇颐二十岁时嫁给他。陆参的生平已无从考证,职方郎中是相当于从六品的小官,他的其他传记资料也没有留下,由此或可推知他的一生并不显赫。陆氏为周惇颐生下长子周寿,于嘉祐三年(1058)周惇颐四十二岁的时候去世。[9]
3.妻子蒲氏(德清县君)。继室蒲氏是蒲宗孟的妹妹。蒲宗孟比周惇颐年少十岁左右,是皇祐五年(1053)的进士,后任翰林学士,并于元丰五年(1082)高升至相当于副宰相的尚书左丞,但仅仅一年后就左迁汝州知事,在辗转担任多地知事之后,卒于知大名府(今河北南部)任上。嘉祐四年(1059),由于景仰周惇颐的品行,蒲宗孟将妹妹嫁给了他。其时周惇颐四十三岁。蒲氏为他生下次子周焘。蒲氏于何时去世并不清楚,从蒲宗孟《先生墓碣铭》[10]称“德清县君”可知她在周惇颐之前去世。
我们并不清楚周惇颐的两位妻子是何时被合葬在一起的。不过就陆氏而言,她去世时,周惇颐正以合州(今四川)签曹判官厅公事的身份赴任四川。她可能被暂时埋葬于某处,熙宁四年(1071)以后再移葬于此。
4.周惇颐。如上所述,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惇颐五十七岁时去世。随后十一月二十一日按其遗言,他被葬于母亲郑氏墓左侧,一如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所记载的:“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母大人之墓左,从遗命也。”葬于母亲墓侧的遗言较为罕见,由此也可看出周惇颐对于母亲的深情。
二、对周惇颐的表彰及其墓的修复
1.南宋
南宋建立后不久,周惇颐便受到了朱熹、张栻(1133~1180)等以道学士人为中心的群体的推崇,对其的某种“表彰运动”也由此开始了,尤其是淳熙年间以降更为显著。道学家们竞相在与周惇颐渊源颇深的地方的州县学或书院里奉祀他,借此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正当性的根据。这些从南宋版《文集》和《濂溪志》为数众多的《祠记》《祠堂记》中便可窥知。以下举出其中几个显著的例子。
如淳熙二年(1175)冬,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詹仪之在韶州曲江县(今广东省)建立周惇颐祠之际,张栻为其撰写了《祠堂记》。[11]同年,静江府知事张某在府学的明伦堂之侧建立“三先生祠”,张栻也为其撰写了《祠记》。[12]“三先生”即周惇颐和二程。上述祠堂均供奉有周惇颐的画像。淳熙五年(1178),张栻还为周惇颐出生地道州营道县(舂陵)重修的祠堂撰写了《祠堂记》。这所祠堂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兴建的祠堂基础上重修、扩建而成,据称达到了“堂四楹”的规模,堂中央供奉有周惇颐和二程的画像。[13]
而在江州(九江)的庐山山麓,江州知事潘慈明与通守吕胜己于淳熙三年(1176)重建了濂溪书堂。濂溪书堂原为周惇颐的住处,当时已经荒废。重建的翌年即淳熙四年(1177)二月,朱熹为此写了《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文中写道:
先生姓周氏,讳惇颐,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渓,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记之。[14]
此后,朱熹每当读到周惇颐之书便想要拜访江州和庐山,对周惇颐的为人仰慕备至。
两年后的淳熙六年(1179)三月,他成为周惇颐曾担任过的南康军知事,由此得以前往江西,实现上述愿望。四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建立周濂溪祠,供奉他的画像,并以二程配享。朱熹《文集》中的《奉安濂溪先生祠文》即为那时所读的祭文。[15]张栻也为此寄来了《祠记》。[16]此外,据记载朱熹在此期间踏访了周惇颐的遗迹,由此可推断他应该也到过周惇颐墓。[17]五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刊行了周惇颐的《太极通书》[18],十月,复兴了白鹿洞书院。[19]
这样,南宋中期道学家们的表彰运动极大地突出了周惇颐的存在。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应魏了翁等人的请求,周惇颐被朝廷赐予“元”的谥号。[20淳祐元年(1241),南宋朝廷将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并追封周惇颐为汝南伯。[21]不用说,这意味着始于周惇颐的朱子学(道学)的系谱亦即“道统”的确立,周惇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在这前后,嘉定十四年(1221),朱熹门人度正收集周惇颐的遗文编成《文集》。[22]至于墓,则在端平元年(1234)得到修复,并设置了祭田。[23]宝祐元年(1253),在墓右侧筑室,并置周惇颐像于其内。[24]
2.从元明清
对周惇颐表彰的势头在元代以降依然持续。元代延佑六年(1319),加封周惇颐为道国公,明代正统元年(1436),修复其祠堂和墓地,并给予其后人以恩惠。[25]
弘治三年(1490),九江府知事童潮修复杂草覆盖的墓地,在墓前修建三间祠堂,安置周惇颐的像,并挂上“宋元公濂溪先生祠”的匾额。另外设立“爱莲室”三间,在其前面开凿池塘,种植莲花,并设立了祭田。[26]弘治十六年(1503),江西督学副使邵宝将祭田扩大,并将周惇颐后代周纶从道州迁来管理祭祀。[27]正德六年(1511),傅楫修复了墓地和祠堂,并增置祭田。[28]紧接着正德七年(1512),廖纪拨出“公廪陶甓数万”,用了两个月时间修葺了墓区。[29]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修复中,则刻上了“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的文字。[30]
清代咸丰五年(1855)二月,罗泽南与李续宾修葺了墓地。[31]罗泽南(1807~1856)是湖南湘乡县人,在太平天国军兴之际,他组织的乡勇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主力部队,他也以此闻名。在九江附近激战之余,他拜访了周惇颐的墓地,并命人将其修复。他虽然身为武将,但朱子学的修养却很深,而且著述颇丰。李续宾是其部下和同乡。[32]他们同为湖南的出身,无疑有意表彰乡土先贤周惇颐。
总而言之,自南宋至清代,历代王朝和士人乡绅对于周惇颐墓的维护和修复,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三、清末光绪年间的整修
周惇颐墓的整修,以彭玉麟及其部下在光绪九年(1883)完成的大规模扩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彭玉麟编辑的《希贤录》对此进行了记载,本文以下主要据此进行叙述。
《希贤录》刊本共上下二卷,上卷二十二叶,下卷十四叶,内题下有“衡阳后学彭玉麟谨辑”,并有光绪九年(1883)春三月彭玉麟的序文。在卷首《濂溪墓图》所附的《说》中,写着“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可见该书是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秋天到冬天期间刊刻而成的。各卷末写着“桐城存之方宗诚/善化麓樵胡传钊分校”“正江与吾李成谋/益阳燕山丁义方合刊”。[33]另外毋庸赘言,《希贤录》这个名字来源于周惇颐《通书》中“士希贤”一语。
编者彭玉麟(1816~1890)是湖南衡阳人,又名玉麐。他与前述的罗泽南都是湘军武将,他在曾国藩领导下创建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屡建战功,官至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并制定了湘军水师营制。光绪九年(1883)编辑《希贤录》之际他已是任职兵部尚书的高官。
丁义方是湖南益阳人,李成谋是湖南芷江人,两人均是彭玉麟麾下的武将。光绪九年(1883)丁义方是湖口镇总兵,李成谋是长江水师提督[34],胡传钊是江西新昌县知县[35]。方宗诚是安徽桐城人,《汉学商兑》作者方东树的族弟,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与朱子学有着共鸣的学者。[36]
卷首的《濂溪墓图》如图1所示。
附于其后的丁义方的《说》,叙述了此次修复的详情。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濂溪周元公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许,系隶德化县属之德化乡清泉社,地名栗树岭,亦名三起山,即庐阜了髻山西北之分支也。墓虽面莲花峰,而相去二十余里,《廖记》所称窆于清泉社莲花之岑,《罗记》所称墓在浔城东南莲花峰下,皆误。义方始闻德化知县刘君长景之言,得确知元公墓所。暨于光绪辛巳,随侍彭大司马率同正任新昌知县胡君传钊,往谒之,乃定集赀修墓之举,自壬午夏经始,洎癸未春蒇事。计拓垣围长八十余丈,高视旧加倍,深其址,而石累以甓而增厚焉。宰木数十株,周环于内,墓之〓磈原罅也,则规石而封之。前有祠,明季已毁于兵。今且濂溪祠与书院遍天下,复可不亟。遂度祠基,建舍于左右,俾奉守者有栖息,展礼者有斋沐之处。崇高其门,而坊表之,自门至墓,级石为道。旧有碑仍之,新立碑四,中为元公母仙居县郑太君墓,左为元公墓,右为元公配缙云陆县君,继配德清蒲县君墓,皆彭公所敬题。义方则谨摹元公遗像,兼图所爱莲花于石,以表洁而遗芳,庶俾过墓则式者有所宗仰乎。工竣以告彭公,为之记。彭公复以征考文献有系于元公最要者,辑为《希贤录》,命胡君传钊继方存之先生分校督刊。义方亦遵命绘锲《墓图》,且为《说》以附于后。抑更有说者,圣贤道大原无不包,以墓为元公体魄所藏,则任修毋嫌越俎。况有京兆赵将军重修濂溪祠宇之例,在责何敢辞。但不为希贤君子所讥,斯为幸耳。时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
上文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1.厘清了周惇颐墓的正确位置,并指出了廖纪《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和罗泽南《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里记述的错误。
2.“光绪辛巳”亦即光绪七年(1881)彭玉麟率江西新昌县知县胡传钊等前往墓地,并制订对其进行修复的计划。
3.“壬午夏”亦即光绪八年(1882)夏修复工作开始,“癸未春”亦即次年光绪九年(1883)春竣工。
4.围墙长度达八十余丈,高度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一倍,墙基也挖得更深,并在墙顶盖上了瓦,墙体也进行了加厚。
5.种植几十株树木,将周围围起来。
6.在出现了裂缝的坟墓土堆上盖上了切割整齐的石块。
7.墓前原有的祠堂毁于明末的战火,在其左右建立屋舍,以供守墓者休息和祭祀者斋戒沐浴之用。
8.将门加高,且竖立牌坊。
9.铺设从门到坟墓的石板路。
10.在原有石碑的基础上,新建了四块石碑。中央是周惇颐之母郑氏的墓碑,左侧是周惇颐的墓碑,右侧是周惇颐妻子陆氏和蒲氏的墓碑。墓碑表面均由彭玉麟题字。
11.石碑上刻有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以及莲花。
12.彭玉麟将有关周惇颐的主要文献整理成《希贤录》,并命胡传钊、方宗诚等校勘之后将其出版。
13.《希贤录》中,由丁义方画了墓区示意图,并附以解说。
14.在上述引文之外,根据彭玉麟的《重修周子墓碑记》还可了解到,他在原有墓碑题词“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中加上“元公”二字。
由上可见,这是一次规模极大的修复。在竣工后的光绪九年(1883)六月四日,彭玉麟率文武宾客幕僚数十人前往拜谒,并进行了祭祀。[37]
四、常盘大定的调查
彭玉麟整修之后,周惇颐墓的面貌维持了很长时间。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在彭玉麟整修后的三十九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査。他拍摄的照片收入《支那文化史迹》,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情形。
常盘做了如下的记录:
周濂溪墓
江西省九江市南十里铺,有周濂溪墓,其位置在十里铺往左转走大约五里处。穿过横梁上写着“元公周夫子墓”的石门,就是墓地的大门。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其缘由或许在于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登上大门内的石阶,就是周濂溪的墓。周围环绕着石墙,墓前有三块碑,左右有两块碑,周子墓上所刻的内容如下:
濂溪先生像赞
道脉
先贤宋元公濂溪周子墓 光绪癸未
宋赠仙居县太君周子母郑太君墓
宋赠缙云县周子元配陆夫人
德清县周子继配蒲夫人 墓
在将这个墓围起来的石墙的中央,有如下三块碑:
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 嘉靖甲寅
重修濂溪周子墓碑 咸丰甲寅
太极图
笔者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二十八日访问此地的。
常盘当时拍摄的照片如图2、图3所示。
若将这两幅图与图1的《濂溪墓图》及其解说对比,可以看出常盘当时所见的墓地,与后者所记载的光绪时代的情形非常吻合。高大的门以及围墙,覆盖在坟墓上的石块,刻在石碑上的周惇颐像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此外,墓前并立着的三块碑,中间是母亲郑氏的墓碑,左边是周惇颐的墓碑,右边是两位妻子的墓碑。周惇颐墓碑上“元公”二字也是彭玉麟整修后的样子。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也在他墓碑左边(从前面看则在右侧)的碑上。如丁义方解说里提到的,遗像旁边刻着《濂溪先生像赞》,这些都延续了光绪时代的光景。
此外,常盘还提到围墙中央的三块碑,写着“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嘉靖甲寅”和“重修濂溪周子墓碑咸丰甲寅”的两块不外乎就是前述明嘉靖和清光绪时所立的两块碑。这两块碑就是图2左后方嵌入墙体的碑。常盘说周惇颐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但原因并不在于他说的“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而是清末声名显赫的彭玉麟对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整修,才有了这样的规模。
结语:鲁迅、周树人、周恩来及“文革”以后
本文追溯了周惇颐墓漫长的历史,最后对从“文化大革命”至今的情况做一考察。
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笔者留学北京大学期间的1983年5月14日到访了此地。那次漫长的独自旅行的路线是:北京—南京—镇江—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上海—九江—庐山—九江(周惇颐墓)—汉口—北京。根据笔者当时的日记,在从九江市内前往墓地的巴士上,向旅客询问周惇颐墓的情况,得到了“现在就算去的话,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之类的回答,由此引来大家纷纷议论。下了车以后沿着田间小路,朝着像是墓地的方向走去,在洼地中心人工堆放的土就是周惇颐的墓地。周围杂树丛生,建筑物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瓦。如果不向当地人请教,根本不知道这就是周惇颐墓。展现在眼前的风景,与随身带来的常盘著作复印件上的截然不同。询问当地人,他们均说墓是在“文革”中被毁坏殆尽的,笔者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不过从墓地往南远眺庐山的风景,确实非常美丽,当地人对此也都如是说。
不过正如开篇所述,在那以后墓被修复一新。就其经过,以下根据墓地中的碑文《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资料1)加以说明。
周惇颐墓在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文革”中被破坏,只剩下墓穴而已。不过“文革”结束后周氏后裔便为修复而奔走,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会从政府和民间募集到20万元,首先复原了墓冢和围墙等。2004年由其后人出资举办“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设立了“修墓委员会”,委员会向海内外的周氏后人募集约200万元的捐助,在九江市政府支持下,对墓进行了全面的修复,从而恢复了往昔的盛况,整个墓区面积达四千余平方米。(图4、图5)
宗亲会尽可能将墓地复原回彭玉麟当时整修的样子。但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周惇颐母亲和两位妻子的墓碑上都有“公元一九九九年九月日重立”的字样,在母亲的碑左侧的那块碑上,虽然刻着周惇颐的像,但没有了常盘大定照片上“濂溪先生像赞”的文字。只有周惇颐的墓碑上刻着“后学衡阳彭玉麟敬题”的文字,可见这应是光绪时代的原样。此外,背后的石墙上确实嵌入了三块石碑,上面是《太极图·图说》《通书》和《爱莲说》。本来这里嵌入的应是嘉靖年间“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和咸丰年间“重修濂溪周子墓碑”,但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墓区的展览馆里竟然陈列着本文多次提到的潘兴嗣《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并且是刻在石板上的原物。从带领我们参观的许家星那里得知,这是近年从田里发掘出来的。墓志铭原来埋在墓前,可见北宋周惇颐将母亲从润州改葬到这里时,也将墓志铭一起移过来埋藏于此了。这几乎就是周惇颐墓唯一遗留至今的原物,无比珍贵。假如没有“文革”的破坏,这块墓志铭一直埋在地里的话,人们就连它的存在本身都不知道吧。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还有一点,参观了展览馆才知道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以及周恩来均是周惇颐的子孙。挂着“周氏家谱展”匾额的展览馆里,与新的周惇颐坐像摆在一起的有《周氏后裔名人介绍》,其中就包含了上述几人的展区。展出的还有几种《周氏宗谱》。另一个展馆挂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爱莲堂”匾额。现在笔者无暇考证他们的家系,但是他们作为周惇颐子孙的事实应该没有错吧。
因为向来鲜为人知,所以在此提及,希望引起世人的注意。
笔者在此再次惊叹于“文革”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可怕破坏。方宗诚在光绪年间修复周惇颐墓之际提到,咸丰以后战乱频仍,庐山的很多名胜以及佛寺都遭到破坏,而周惇颐墓的树木、石碑以及坟堆等都并未受损,即便是盗贼,也不敢破坏墓地。[39]就算在清末大乱期也保存下来的墓,却在“文革”期间遭到了真正的毁灭。不得不说,即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像“文革”这样无情破坏文化的例子也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在深入推进对传统文化包括儒教的再评价,周惇颐墓的修复也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持。靠近墓的南边的崭新的道路,还被命名为“濂溪大道”。附近还有“九江濂溪宾馆”“濂溪农贸市场”。墓的西边近处有一座于2000年兴办的九江学院,在这所大学偌大的校园里挖掘了一座很大的爱莲池,还立了周惇颐的像。登录九江学院的网站就能看到,这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71年建立的“濂溪书院”(准确说应是“濂溪书堂”),濂溪书院在清末1902年改称九江中学,成为现在九江学院的前身。以上所述,可以说都在诉说着中国正致力于再度“盛世修文”的动向。
资料1《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颂濂溪
——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古今皆然。今重修濂溪墓,以承先人之遗风,夙后世子孙之愿,供仰慕者以瞻。
濂溪墓历千年沧桑,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毁于“文革”、仅存墓穴。“文革”后,族裔周观源奔走四方,呼吁修复。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周国枚、国材、楚阶、汉明等来浔谒祖,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与之连手,以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捐计20万元,完成了一期墓冢、围墙、照壁的复原。2004年苏州鸿利机电设备公司董事长周斌炎出资召开“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成立修墓委员会,由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周楚阶担任委员会主任。他广结善缘于海内外,联同美国侨领周谦益、苏州周斌炎、重庆周厚勇等,共筹款200万元左右,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主任吴宜先积极支持,组织全面修复,终使墓园焕然于世。
濂溪先生,理学鼻祖,图说太极,诠释周易;胸中洒落,光风霁月;道德文章,千古流芳。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今景观已复,而道脉重传,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特为之记以志其盛。
周氏宗亲重修濂溪祖墓委员会
顾 问:吴锦萍 郭建林 周仪 周谦益 周炎沐 周汉彬 周国枚 周国材 周汉明 周振基 周炳树 周国屏 周朝宜 叶伟平
主任委员:周楚阶
常务副主任委员:周斌炎 吴宜先 周厚勇
副主任委员:周黄丽英 周厚立 周开泉 周志峰 叶筱慧 周桂洪 周日新 周镇隆 周锡强
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立
(作者单位: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
附注
注释:
[1]参见拙作:《儒家道德实践理论新诠》,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147~176页。以及《程伊川、朱子“真知”说新——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观点看》,《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2期,2011年12月,第177~203页。
[2]“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了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了自家意。”(《传习录·下》)
[3]阳明说:“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原。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传习录·上》)
[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第402页。
[5]同上。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2003年,第403页。
[7]唐君毅:《由朱子之言理先气后论当然之理与存在之理》收录《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年。
[8]此意亦依唐先生的说法,唐先生认为对于理的了解、肯定与依理而行,三事是“相持而共长”的。唐先生此义见于前注之论文。拙作:《唐君毅先生对朱子哲学的诠释》,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第143〜166页。
[9]《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上册,卷二十五,第317页。
[10]张载:《正蒙•诚明篇》。横渠又曰:“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篇》)
[1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册二,卷十五,第302页。
[12]同上。
[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册二,卷十五,第303页。
[14]同上书,第303〜304页。
[15]牟先生对此条做评论认为,由此问答可知朱子亦明觉到知至不必一定能意诚;又真知可从“他律之行”验之。(《心体与性体(三)》,第404〜405页)按:既然朱子认为魏椿所回答的“知之未极其至”是对的,则朱子不会认为知至不必能意诚;而真知的确可以用能否表现出道德行为来检验,牟先生后一解应合于朱子意。但从明理而诚意,又表现出道德行为,此是否为“他律之行”?则可以再考虑。
[16]朱熹:《答李孝述继善问目》,《晦庵续集》,卷十(《四部丛刊》),第89页。
[1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册二,卷十七,第382页。
[18]以上三条都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册二,卷十七,第384页。
[19]朱熹:《答陈同甫》,《朱子大全》,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卷三十六,第21页。
[20I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第一章,牟宗三先生:.《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册),第178页。
[21]见拙著《从牟宗三先生康德第二批判的诠释看康德与朱子的思想型态》,“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深圳大学,2013年11月16〜18日。
注释:
[1]朱熹:《近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2]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页。
[3]同上书,第163页。
[4]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7页。
[5]朱熹:《近思录》,第16页。
[6]参见赵金刚:《动静生生与“理生气”》,《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
[7]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1~203页。
[8]朱熹:《朱子语类》,第71页。
[9]同上书,第2页。
[10]朱熹:《朱子语类》,第2~3页。
[11]同上书,第106~107页。
[12]同上书,第6页。
[13]同上书,第7页。
[14]《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15]当然,《朱子语类》中的确有“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这样的说法,但详读那段文字,显然是在强调“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不是说另有静之理和动之理。
[16]朱熹:《朱子语类》,第2376页。
[17]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第112页。
[18]朱熹:《朱子语类》,第2372页。
[19]同上书,第2375页。
注释:
[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七章,尤其第192~193页。
[2]韩国学者孙炳旭在比较李滉(1501~1570)、曹植(1501~1571)、李珥(1536~1584)和崔汉绮(1803~1877)等人的静坐观之后,认为,李愰属于道问学的居敬穷理的静坐观,曹植属于尊德性的主敬行义的静坐观,李珥则强调未发时的涵养功夫,崔汉绮是从气学切入的涵养省察论。参见所著:《韩国儒学之静坐法》。如其说成立,则栗谷的未发功夫论在朝鲜儒者中就颇有特色。
[3]《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8页。
[4]在列举有关涵养的条目之前,栗谷有一个解释,说:孟子所谓存养,通贯动静而言,即诚意正心之谓。但先贤论静时工夫,多以存养涵养为言,故采其切要之语录之如左。(《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栗谷没有使用“未发工夫”这样的字眼,但从他所采之语来看,基本上都是讨论未发工夫的,详下正文。
[5]见程子语2.或问:“喜怒哀乐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6]所谓被动地闻见,意思是当外物与耳目这些闻见器官接触时(即“物之过乎目”“过乎耳”),这些器官自动地做出一种类似本能的反应,比如,一个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目击了一起交通事故。可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这个证人很有可能来不及做出反应,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心理学实验表明,只有有意识地去观察,才谈得上观察,观察才能有得。设想课堂上一个心不在焉的学生,要是问他,老师刚才都讲了一些什么,板书了什么,很可能他答不上来,顶多说“好像是说……,好像写了……”那么,这个学生所说的“好像……”就是他的所见所闻?所以,这个时候仍然可以说有见有闻?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一个学生即使上课时心不在焉,他也多少有所见闻?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他的闻见器官甚至思维器官都仍然处于工作状态。
[7]宋元时期,佛道学者在讨论调心之法时,常常涉及如何处理闻见觉知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当是刺激理学家讨论未发已发时重视闻见觉知问题的一个外缘。宋代雪窦禅师(重显,980~1052)有一首著名的颂,为许多佛教典籍所收:“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澄潭照影寒?”(《碧岩录》卷四,《指月录》卷八)又,北宋石门元易禅师有一段论心空的话,亦经常为人提及:“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大众,只如闻见觉知未尝有间,作么生说个心空底道理?莫是见而不见,闻而不闻,为之心空邪?错!莫是忘机息虑,万法俱捐,销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归法界,为之心空邪?错!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未审毕竟作么生?还会么?”(《五灯会元》卷十四,亦见《指月录》卷二十七,《续传灯录》卷十二)又,宋人张嵲(1096~1148)作《法界颂》二首,其二云:“山河大地因谁有?闻见觉知非我亲。不挂一丝全体露,真成本分住山人。”(《紫薇集》卷九,四库全书本)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王喆,1173~1170)论降心之道云:“凡降心之道,若湛然不动,昏昏默默,不见万物,杳杳冥冥,不内不外,无丝毫念想,此是定心,不可降也。若随境生心颠倒,寻头觅尾,此名乱心,败坏道德,损失性命,不可纵也。行住坐卧,常勤降伏,闻见觉知,此为病矣。”(《重阳立教十五论·第八论降心》,此据[清]郭元釪《全金诗》卷六十,四库全书本,同时参考了[明]阳道生《真诠》上,明嘉靖刻本。正统《道藏》本,字句有异,相较之下,前者胜之,故取彼而舍此)
[8]原文见《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2页。
[9]牟宗三看到了此章第6节与第8节之间的矛盾:“夫前既言‘怎生言静?’,今又言‘谓之静则可’,不觉其矛盾乎?”,“若根据前‘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之语,则因‘须有物’当即不得谓静矣!如此颠三倒四,为动静所困,总闹不明白,此其所以认为‘难’也。”(《心体与性体》第三部第二章,第316页)其说不为无见。遗憾的是,他对第11节的问题却轻易放过了。在其书中,他将此章第10节以下至结尾单列为一段,与此下两条以及从《遗书》卷十五选来的一条(“人多思虑”)并列,称赞此四条“察识亦颇精,言之亦颇亲切”。(《心体与性体》第三部第二章,第319页)则未免读书偶一失察。
[10]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疑处,朱子还提到,“所谓‘无时不中’者[按,即此章第4节:曰:“中是有时而中否?”曰:“何时而不中?以事言之,则有时而中;以道言之,则何时而不中?”(《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所谓‘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按,此即第5节:曰:“固是所为皆中,然而观于四者未发之时,静时自有一般气象,及至接事时又自别,何也?”曰:“善观者不如此,却于喜怒哀乐已发之际观之。贤且说静时如何?”(同上)],则语虽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无断续。至其答‘过而不留’之问[按,此即第12节:或曰:“当敬时,虽见闻,莫过焉而不留否?”曰:“不说道非礼勿视勿听?勿者禁止之辞,才说弗字便不得也。”(《遗书》卷十八,第202页)]则又有若不相直而可疑者。”(《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62页)
[11]当然,朱子对此章也非完全否定,除了正文中提到的,他有取于第8节、第11节后半截之义理,他还肯定了第9节(“答敬何以用功之问”)与第10节(“答思虑不定之问”)。参见:《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
[12]许渤事见《遗书》卷三:许渤与其子隔一窗而寝,乃不闻其子读书不读书。先生谓:“此人持敬如此。”(曷尝有如此圣人。)(《二程集》第65页)朱子如此解读此条,亦未有十分根据。从经验上看,许渤之事并非无可能。如果一个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于自身,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是有可能毫无察觉的。
[13]见程颐答苏季明问:或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页)栗谷采用了这条材料,文字略有改动:(程子语4.)苏昞问:“于喜怒哀乐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却又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圣学辑要》三“修己第二中”,《栗谷全书》卷二十一,第11页)
[14]必须说,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了解《中庸》所说的未发已发与闻见知觉问题不相干的,因为,他在批评吕子约有关未发无见闻的说法时就曾指出:“子思只说喜怒哀乐,今却转向见闻上去,所以说得愈多,愈见支离纷冗,都无交涉。”(《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35页)
[15]“九思”之“思”,一般理解为“思惟”“思虑”,详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三季氏,第1160页。谢良佐则将其理解为“省察”工夫:“未至于从容中道,无时而不自省察也。虽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谓思诚。”(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第173页)
[16]郑玄在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这句话做注时说:“容当为睿。睿,通也。心明曰圣,孔子说休征曰:圣,通也,兼四而明,则所谓圣。圣者,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转引自[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八《郊社考》二十一,清浙江书局本。“则所谓圣圣者”六字,疑当作“则所谓圣者”,两“圣”字,有一为衍出。孙星衍即做此解,参见所著《尚书今古文注疏》“洪范第十二上周书三”,清平津馆丛书本。)按:郑玄所引“孔子说休征”云云,不见经传,然“休征”一词语出《洪范》“九畴”之八“庶征”条,与“咎征”相对,意为“美行之验”,包括五种征验:肃时雨若、乂时旸若,晢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在人事与天时之间建立起感应关系:肃—雨,乂—旸,哲—燠,谋—寒,圣—风。伏胜(前260~前161)在写《洪范·五行传》时,有意识地将“敬用五事”与“休征”当中的人事术语联系起来:“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谓不肃”,“次二事曰言,言之不从是谓不艾”,“次三事曰视,视之不明曰不哲”,“次四事曰听,听之不聪曰不谋”,“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五行传》,四部丛刊本)。董仲舒(前179~前104)《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将“敬用五事”的实践者明确为“王”:“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从,从者,可从;视曰明,明者,知贤不肖者,分明黑白也;听曰聪,聪者,能闻事而审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无不容。”(转引自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洪范第十二上周书三”)。孔安国(前156~74)在注《尚书》“休征”一段时,吸收了伏胜与董仲舒之说,把“庶征”理解为君王行事之验,同时,还把“圣”解释为“通理”:“君行敬,则时雨顺之”,“君行政治,则时暘顺之”,“君能照哲,则时燠顺之”,“君能谋,则时寒顺之”,“君能通理,则时风顺之”([汉]孔安国《尚书注疏》附释音,卷第十二,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则郑玄之解“圣”为“通”,似乎亦有所本,并非杜撰。
[17]未发时无见无闻的情况,在朱子看来,容或有之,但他似乎认为,那只是极少数,他有些不屑地将其称作“神识昏昧底人”(《答吕子约第四十五书》,《文集》卷四十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35页)。
[18]吕大临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则赤子之心。当其未发,此心至虚,无所偏倚,故谓之中。以此心应万物之变,无往而非中矣。”(《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7页)程颐回应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赤子之心,发而未远于中,若便谓之中,是不识大本也。”(同上)盖伊川认定,赤子之心为已发,可以谓之和,但不可以谓之中。(《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8页)吕大临则为自己辩解说,“今言赤子之心,乃论其未发之际”(同上)。不难看出,伊川与与叔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对赤子之心的定位不同,一个以之为未发,一个以之为已发,而之所以有此不同,实缘于他们两人对心的理解不一,伊川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8页),而与叔则质疑:“然则,未发之前,谓之无心,可乎?”(同上)吕与叔的这个质疑非常有力,以致伊川最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话:“‘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与吕大临论中书》,《文集》卷九,《二程集》,第609页)
[19]在朱子哲学中,未发已发的一个含义是性情,未发指性,已发指情。理学相信,人物之性皆禀之于天理,有所谓“理性”之说。
[20]陈来:《中和旧说年考》,《朱子哲学研究》,第168页。
[21]《延平行状》撰于隆兴二年甲申(1164)正月,朱子35岁。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卷上,第317页。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3]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韩〕李珥:《圣学辑要》,收入《栗谷先生全书》,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MM&url=/itkcdb/text/bookListIframe.jsp?bizName=MM&seojiId=kc_mm_a201&gunchaId=&NodeId=&setid=50852。
[5]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本。
[6]吕大临:《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7]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8]钱穆:《朱子论静》,《朱子新学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第2册,第405〜427页。
[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0]陈荣捷:《朱子与静坐》,《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204页。
[1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2]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13]陈来:《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收于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附录,第390〜415页。
[14]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5]〔法〕谢和耐:《静坐仪、宗教与哲学》,耿升译,收于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辑,第 224 〜243 页。
[16]〔日〕吾妻重二:《静坐考——道学の自己修养めぐって》,收入同论集刊行会(编)《村山吉广教授古稀记念中国古典学论集》,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第753〜778页,亦收入所著《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东京:创文社,2004年。
[17]〔日〕藤井伦明:《日本研究理学工夫论之概况》,收于杨儒宾、祝平次(编)《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 312 〜313 页。
[18]杨儒宾:《宋儒的静坐说》,《台湾哲学研究》,第4期,2004年3月,第39〜86页。
[19]杨儒宾:《论“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5卷第 3期(2005年),第33〜74页。
[20]〔日〕中嶋隆藏著,陈玮芥等译:《静坐——实践与历史》,新竹: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1年。
[21]杨儒宾、马渊昌也、艾皓德编:《东亚的静坐传统》,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
[22]〔韩〕孙炳旭:《韩国儒学之静坐法》,姜雪今译,收入杨儒宾等(编)《东亚的静坐传统》,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
[23]史甄陶:《东亚儒家静坐研究之概况》,《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2期(总第16期),201I年12月,第347〜374页。
[24]〔日〕高桥进:《李退溪与主敬哲学》,王根生等译,延吉市: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
[25]〔韩〕李承焕:《朱子修养论中未发的涵义——心理哲学的过程及道德心理学上的涵义》,http://homepage.ntu.edu.tw/~philo/Chinese/conference/200607korea/ рр/403 .htm。
[26]Liu,Shu-hsien.“On Chu Hsi s Search for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in Harmony and Strif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 ed. Shu-hsien Liu and Robert E. Allins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8, pp.249 〜270。
注释:
[1]朱子晚年强调:“吾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正心诚意)。”(《文公朱先生行状》,《勉斋集》卷三六)如果说“格物致知”是朱子哲学的理论基石,那么“正心诚意”则是朱子哲学的行动纲领。朱子也说:“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
[2]朱熹:《答宋深之(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近思录>提要》。
[4]朱熹:《大学章句》。
[5]朱子说:“致知、格物,只是一个。”(《朱子语类》卷十五)格物致知“只是一本,无两样功夫也。”(《答陈才卿(五)》,《朱文公文集》卷五九)陈来先生指出,朱子所说的“致知”只是主体通过考究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致知作为格物的目的和结果,并不是一种与格物并行的、独立的、以主体自身为认识对象的认识方法或修养方法。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
[6]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
[7]《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8]同上书,卷十六。
[9]同上书,卷十八。
[10]《朱子语类》卷十六。
[11]同上。
[12]同上。
[13]“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14]《朱子语类》卷十七。
[15]《孟子集注》卷十三亦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16]《大学章句》。朱子在淳熙乙酉年(1189)三月序定《大学章句》。
[17]《答李孝述继善问目》,《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五。此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
[18]《答江元适(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此书作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这是朱子首次对全体大用思想的诠释。
[19]《答许顺之(十四)》,《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此书作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20]《答张敬夫(三十五)》,《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此书作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
[21]《朱子语类》卷十八。僩指沈僩,戊午(1198)以后所闻。
[22]《朱子语类》卷六。道夫即杨道夫,己酉(1189)以后所闻。蜚卿为童伯羽,庚戌(1190)以后所闻。
[23]《朱子语类》卷十八。人杰即万人杰,庚子(1180)以后所闻。
[24]刘宗周:《论语学案》卷八。
[25]《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贺孙即叶味道,辛亥(1191)以后所闻。
[26]《答余国秀(二)》,《朱文公文集》卷六二。此书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
[27]《朱子语类》卷十五。夔孙即林夔孙,丁巳(1197)以后所闻。
[28]《答张元德(一)》,《朱文公文集》卷六二。此书作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
[29]清代李清馥认为朱子之学就是全体大用之学:“因叙述学派而敬书之至朱子之学,内圣外王之要,全体大用之详,前贤述之备矣。”(《文公朱晦庵先生学派》,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六)日本楠本正继博士认为,“全体大用”之思想是朱子思想的中心,在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全体”就是心中包含所有的道理,所谓“大用”就是人心自然能应接万事万物。楠本正继指出:“全体大用思想乃源于所谓:虽然存在于相对的时空中,同时却也要求绝对,并不断试图在人世中,实践此种绝对的人类精神之必然要求,此思想的意义全然在此。”参见柴田笃:《楠本正继博士的朱子学研究》,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7~312页。
[30]《朱子语类》卷十四。
[31]同上书,卷十八。
[32]《答江德功》,《朱文公文集》卷七。
[33]《朱子语类》卷十四。
[34]同上。
[35]同上。
[36]《朱子语类》卷十五。
[37]朱熹:《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38]《朱子语类》卷十八。
[39]同上书,卷六十。
[4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41]同上。
[42]参见拙著:《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以朱熹为中心》,《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
[43]《建宁府崇县五夫社仓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44]《劝立社仓榜》,《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45]朱子“全体大用”思想对陆王心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刘宗周等。在东亚世界,韩国李退溪、李栗谷、丁茶山以及日本山崎暗斋、楠本正继等对朱子全体大用的思想多有阐发。鉴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撰述。
[46]陈淳:《北溪字义》卷上。
[47]《朱子语类》卷十四。
[48]关于朱子的“定性说”,可参见拙著《道学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以宋代“定性说”的展开为中心》,《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9]真德秀:《讲筵卷子十一月八日》,《西山文集》卷十八。
[50]真德秀:《跋刘弥邵读书小记》,《西山文集》卷三十六。
[51]真德秀:《周敬甫晋评序》,《西山文集》卷二十八。
[5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53]真德秀:《西山文钞序》。
[54]《真西山读书记序》。
[55]《朱子语类》卷十四。
[56]同上。
[57]真德秀:《大学衍义札子》。
[58]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一。
[59]胡广等:《大学章句大全》。
[60]李清馥:《熊勿轩先生禾学派》,《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七。
[61]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62]邱浚:《大学衍义补原序》。
[63]邱浚:《进大学衍义补表》。
[64]《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三。
[65]同上书,卷一六〇。
[66]同上。
[67]《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68]Barbara Johnstone.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 Well, 2002.p.l02.
[69]N .Fairclough/ R.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Van Dijk(eds.):Z),sco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London,1997.pp•271 〜280。
[70]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8页。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门人后学研究》(14ZDB008)、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朱子四书学之系列比较研究》(13CZX045)。
[2]黄榦:《勉斋集·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43页。
[3]赵顺孙:《四书纂疏》,长春:吉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84页。
[4]同上书,第87页。
[5]同上书,第346页。
[6]《四书或问》当分成《论孟或问》《学庸或问》两大类别看,参拙稿《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
[7]《四书纂疏》,第363页。
[8]同上书,第102页。
[9]真德秀:《四书集编》,长春:吉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71页。
[10]《勉斋集》,第374页。
[11]《四书纂疏》,第364页。
[12]《勉斋集》,第374页。此处“德”之解尚有初本、定本之争,一说为“行道而有得于身”,一说为“得道于心”,据《集注》下文言“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似乎《四书纂疏》等说更确。
[13]《四书纂疏》,第108页。
[14]史伯璇:《四书管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3页。
[15]《勉斋集》,第509页。
[16]同上书,第589页。
[17]同上书,第422页。《勉斋语录》有相似记录,参《勉斋集》,第789页。
[18]《四书纂疏》,第442页。
[19]《勉斋集》,第464页。
[20]同上书,第466页。
[21]同上书,第464页。
[22]同上书,第350页。
[23]《勉斋集·语录》,第790页。
[24]《勉斋集》,第426页。
[25]同上书,第349页。
[26]同上书,第434页。
[27]《勉斋集·年谱》,第842页。
[28]《勉斋集》,第462页。
[29]同上书,第790页。
[30]同上书,第791页。
[31]同上书,第847页。
[32]同上书,第385页。
注释:
原文《周惇頤の墓一その歴史と現況》载于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開設記念号,2012年3月,第145〜162页。
[1]吾妻重二:《周惇頤について——人脈・政治・思想》,收入氏著《宋代思想の研究——儒教・道教・イ厶教をめぐる考察》,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中文本《论周惇颐——人脉、政治、思想》可参见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
[2]关于本次国际会议的情形,可参井泽耕一:《江右游記——〈哲学与時代朱子学国際学術研討会〉に参加して》,《日本中国学会便り、》,2011年第2号,通卷第20号。
[3]同行前往的是大阪大学的汤浅邦弘、岛根大学的竹田健二和茨城大学的井泽耕一。领路的是南昌大学许家星,在此对其致以谢意!
[4]关于周惇颐的传记,若非特别说明,本文依据的是许毓峰《周濂溪年谱》,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三,1943年,以及注1所揭拙文。
[5]潘兴嗣:《先生墓志铭》及《仙居县大君墓志铭》、蒲宗孟:《先生墓碣铭》,均见南宋版《文集》卷八,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南宋版《文集》卷首。
[6]可参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68页“分司官”条。
[7]周惇颐嘉祐六年(1061)四十五岁时赴任虔州(今江西南部)通判的途中,游玩了庐山,被其美景吸引。他将莲花峰下的小溪命名为“濂溪”,在溪旁建立“濂溪书堂”,此后他惦记着将来何时能到此隐居。可参度正《年表》。(据此,本文末尾提到的九江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濂溪书堂”建立的1061年,而非周惇颐隐退后定居于此的1071年。——译者注)
[8]基于《宋史·职官志十·叙封》中“庶子、少卿监、司业、郎中、京府少尹、赤县令、少詹事、论德、将军、刺史、下都督、下都护、家令、率更令、仆,母封县太君,妻县君,其余升朝官以上遇恩,并母封县太君,妻县君”的制度。这项制度在北宋末的政和三年(1113)被蔡京修改,蔡条《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改郡县君号为七等,郡君者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县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根据这项规定,此后不再用“县太君”或“县君”的称号,而以“宜人”或“孺人”代替。如朱熹的高祖父、曾祖父和祖父均未入仕,凭借朱熹父亲朱松的官职而使他们及其夫人获得“承事郎”和“孺人”的称号。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朱府君迁墓记》,《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四。朱熹母亲祝氏称“先妣孺人”也是依照此制,朱熹:《尚书吏部员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圹志》,《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四。
[9]《周子全书》卷二十所收《进呈本年谱》,财团法人台北市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第390页;陈克明点校:《周惇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8页。
[10]蒲宗孟:《先生墓碣铭》,南宋版《文集》卷八。
[11]张栻:《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南轩集》卷十,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中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794页。
[12]张拭:《三先生祠记》,《南轩集》卷十,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中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707页。
[13]张拭:《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南轩集》卷十,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拭全集》中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698页。
[14]朱熹:《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15]朱熹:《奉安濂溪先生祠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
[16]张栻:《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南轩集》卷十,《张拭全集》中册,第706页。
[17]王懋竑:《朱子年谱》“淳熙六年三月”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1页。
[18]朱熹:《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19]王懋竑:《朱子年谱》“淳熙六年十月”条。
[20]参度正《年表》。
[21]《宋史·理宗本纪》,及《进呈本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所收。
[22]度正:《书文集目录后》,南宋版《文集》卷八。
[23]赵善璙:《濂溪书堂谥告石文》,《希贤录》卷上,有关《希贤录》请参见后文。
[24]何子举:《先生墓室记》,南宋版《文集》卷八。
[25]《希贤录》卷上《历代尊崇典礼》,《周子全书》卷二十一《列代褒崇》。
[26]《童潮濂溪祠墓记》,《希贤录》卷下。
[27]“《庐山志》:了髻山东北为凤凰山、天花井山,西北为栗树岭,其下有濂溪先生墓。”见《希贤录》卷下。《查取后裔赴九江守墓公檄》,亦见《希贤录》卷下。
[28]《傅楫重修墓祠增置祭田记》,《希贤录》卷下。
[29]《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30]彭玉麟:《重修周子墓碑记》,《希贤录》卷下。(彭玉麟原文如此,但据下文常盘大定的记载,“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之下应有一“墓”字。——译者注)
[31]《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32]《清史稿·卷四百七·罗泽南传》,《卷四百八·李续宾传》。
[33]《希贤录》近年被收入俞冰、马春梅编《周濂溪先生实录》第四册(《中国历史名人别传录》2,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影印出版,本文所用即此影印本。
[34]丁义方与李成谋的传记均在《清史稿》卷四百十五中,彭玉麟《重修周子墓碑记》则在《希贤录》卷下。
[35]根据后文将述及的《濂溪墓图》所附的《说》。
[36]《清史稿·卷四八六·方宗诚传》。
[37]方宗诚:《谒周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38]引文出自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踏蹟》“解说下”,京都:法蔵馆,1976年。该书原先以《支那文化史蹟》之名在1940年由法藏馆出版。(常盘大定(1870~1945),日本宫城县人,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古建筑研究者。本文所录图版出自《中国文化史蹟》第十册第44~46页。另,根据希贤录》卷下《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常盘在文中提到的“咸丰甲寅”疑为“咸丰乙卯”之误,因罗泽南修复濂溪墓在咸丰五年乙卯春,而非在此前一年的甲寅年,恐涉上“嘉靖甲寅”而误。——译者注)
[39]方宗诚:《谒周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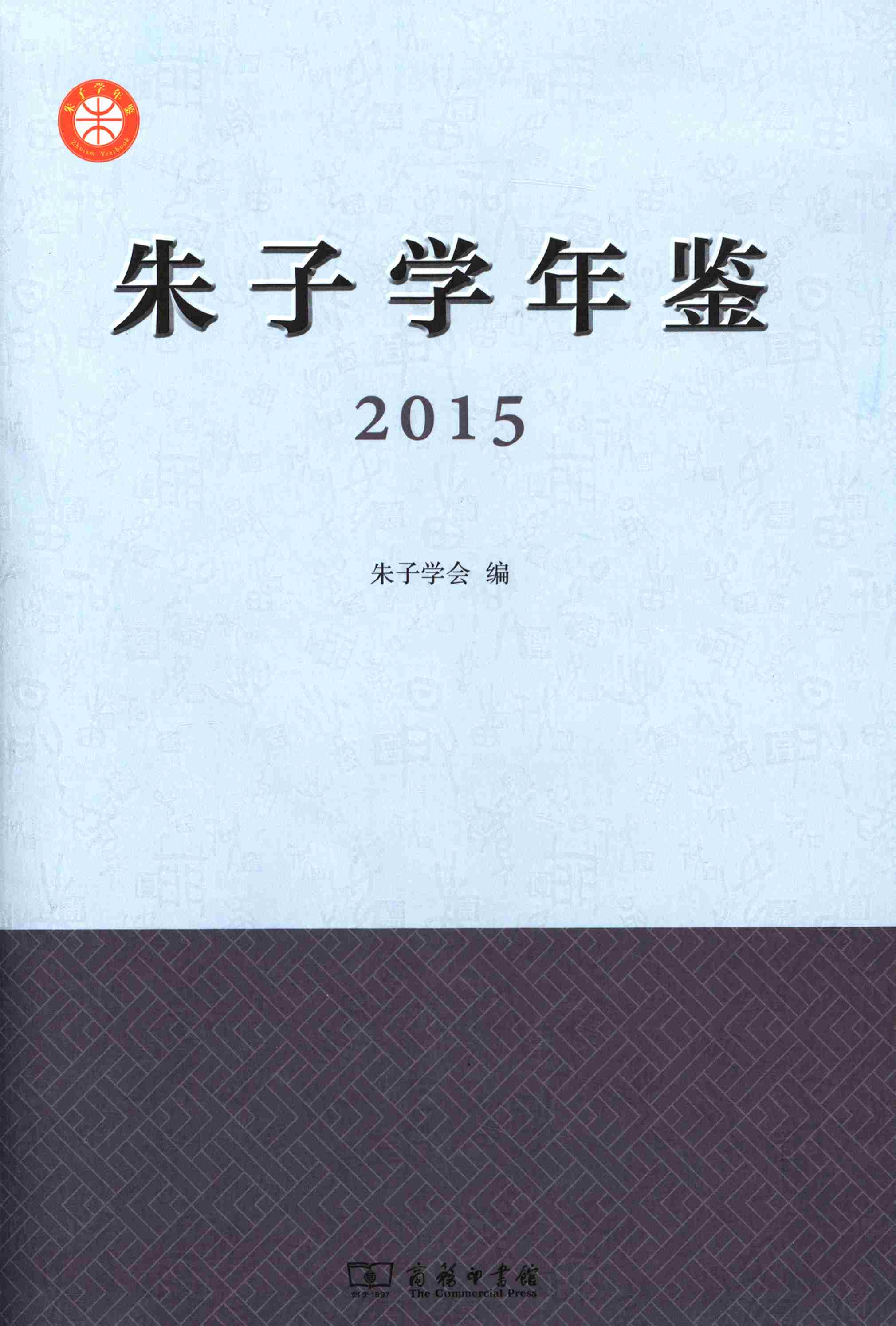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