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07 |
| 颗粒名称: | 特稿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5 |
| 页码: | 1-2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研究特稿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及展望情况。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特稿 |
内容
韩国朱子学新论
——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陈来
朱子心性论对于性情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1],以性为情的内在根据,情是性的外发表现。《孟子》曾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朱子的解释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2]《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子解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3]朱子哲学中的“情”有两种用法,一指四端(《孟子集注》说),一指七情(《中庸章句》说)。四端是道德情感,纯善无恶,七情则泛指一切情感活动,有善有恶。朱子以“四端”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这合于“性发为情,情根于性”的基本原则。而如果说喜怒哀乐等“七情”有善恶邪正,那就碰到一个问题,即七情中发而不善的情感是否也是发于仁义礼智的本性?如果说不善之情也是发于全善之性,这显然是有矛盾的。而且,朱子从未肯定七情中不善者不是发于本性。这是朱子学中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
朱子哲学曾提出,人是由理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退溪根据这一看法,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发自人的形体(气)。退溪“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这一命题的提出,主张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使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李退溪曾与奇大升(高峰)反复论辩,成为朝鲜朝性理学史的一大事件。奇大升反对“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的提法,他认为七情泛指人的一切情感,四端只是七情中发而中节的一部分,因而四端作为部分应与作为全体的七情共同发自同一根源,即皆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奇大升这个说法以朱子《中庸章句》说为据,并可在朱子学体系内找到较多支持,但无法解决朱子心性论自身未解决的问题。在李退溪看来,以为“七情”有两种用法,一种同于奇说,即“以混沦言之”,在这个意义上,四端包容在七情之内,一种则以七情与四端相对而言,以七情为四端以外的其他情感,包括反映人的生理需要的各种情感以及非道德情感等。退溪正是在后一种用法的意义上,认为七情不是发于性,而是发于气。
退溪的说法虽在朱子哲学中所能找到的根据较少,但显然力图在朱子基础上有所发展,使朱子学体系更加完备。同时,他认为四七分理气并不是说四端仅仅是理,七情仅仅是气,四端与七情都是兼乎理气的。他说“二者皆不外乎理气”[4],“四端非无气”,“七情非无理”[5],认为四端七情作为现实情感无不兼乎理气,因为心是理气之合,情也是理气之合,但二者“虽同是情,不无所从来之异”[6],二者作为现实意识或情感虽皆兼乎理气,但就二者所发的初始根源说,四端发自性理,七情发于形气。他说:
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乎气,四端是也。
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乎理,七情是也。[7]退溪认为四端与七情虽然都兼乎理气,但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从性理发出而气顺随加入而成的是四端,从形气发出而理随之乘驭而成的是七情,所谓四七分理气,并不是说四端纯是理,七情纯是气,只是说四端发于理、主于理,七情发于气、主于气。退溪的这一思想,把人的情感区分为反映或适应生理需要的自然情感(七情)和反映社会价值的道德感情(四端),并认为二者形成的根据与方式不同,前者根于人的生理躯体,后者来源于人的道德本性。气随、理乘则指四七构成的方式和发用的机制,这些思想较之以前“理学”的处理更进了一步。
表面上看来,相对于奇高峰的主张,李退溪四七分理气的思想在朱子思想材料中的根据较少,但在实质上,可以认为是对朱子处理道心人心思路的一个扩展。按照朱子思想,人的意识被区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指道德意识,人心则指感性欲念。朱子认为“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8],这也就是认为道心理之发,人心气之发。李退溪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思想应该说是朱子道心人心说应用于情感分析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关于四七分理气的问题,其直接意义是区分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不同来源与根据,并不意味着理发一定为善或气发一定为恶。根源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善恶的分别还决定于人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努力,改善四七的构成方式和发用机制。李退溪说:
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而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9]
所以,四端虽发于理而无不善,但并非一切理发者皆为善,理发的过程中如果因气的冲击而不能保持原来的方向,则流于不善。七情发于气,如果气发的过程受到理的控制与有力引导,则可以为善;如果理不能在气发的过程中及时控制引导,则流为不善。可见善恶之间的关键还在于发作过程中理气的相为胜负。这里说的理气胜负实际上就是指道德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欲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发也,理显而气顺则善,气掩而理隐则恶”[10],只有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使理性能驾驭、控制、引导感性即“以理驭气”11,思维情感才能呈现为善。这些讨论是在四七内在根源的问题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的理发或气发的过程和机制。
可见退溪高峰的理发气发之辩,主要关注的是四七“发于”何处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又涉及了四七“发用”的过程和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退溪和高峰的四七辩论中,所谓理发气发的“发”的讨论包含二义,一个是“发于”,如情发于性;另一个是“发用”,如性发为情。“情发于性”和“性发为情”,这两个命题在表达性情的体用关系上是一致的,而在表达的方向顺序上不同,其中“发”所连接的介词不同,从而造成了有关理发气发讨论的不同意义。在退溪、高峰的讨论中,“发于”的问题是主要的。
朝鲜时代儒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①,但始终没有以四端七情普遍对举成为讨论课题,更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一点上,朝鲜时代性理学是有其贡献的。
二
一般认为,栗谷的思想接近朱子而与退溪的立场相反,集中体现在有关四端七情的讨论。其实,栗谷更多的讨论是围绕道心人心之根源与发动的讨论,其观点和朱子多有不同。而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下面,我们以《栗谷全书》卷十《栗谷答成浩原第一书(壬申)》(数日来道况如何)为基本资料,来梳理、分析栗谷的思想。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复礼,欲穷理,欲忠信,欲孝于其亲,欲忠于其君,欲正家,欲敬兄,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固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揜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渴欲饮,痒欲搔,目欲色,耳欲声,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之人心。其原虽本乎天性,而其发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12]
这一段是解释和说明道心人心的。栗谷从道心人心的界定开始而不是从四端七情的说明开始,表明他首先针对朱子之说。他从《乐记》的感动说开始,首先认为一切欲念的产生都是感动者引起的,而感动者都是形气。道德的欲念是道心,自然的欲望是人心。他认为,就欲念的发生而言,道心出于仁义礼智,而且没有受到形气的遮蔽;人心也是本源于本性,但其发生由乎耳目形气之私。照他的说法,道心、人心都应在本源上出自仁义礼智的本性,只是道心在发生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形气的遮蔽,而人心在发生的过程中受了形气的影响而异变了。这个说法,如果用退溪、高峰的理发气发的说法,在内在根源的意义上,应当属于道心人心皆理发说,就是道心人心都“发自”于理的本性。这就与朱子不同,因为朱子《中庸章句序》主张道心原于性命之理,人心生于形气之私。①
这里还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栗谷所用的“发”字,如“其发也”是指发自,还是发出、发为?是表达未发的根源,还是已发的过程和形态?②
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鞲,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若来书所谓理气互发,则是理气二物,各为根柢于方寸之中。未发之时,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发则为道心,气发则为人心矣。然则吾心有二本矣,岂不大错乎。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吾兄何从而得此理气互发之说乎。其所谓或原或生者,见其既发而立论矣。其发也为理义,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理义之心乎。此由于性命在心,故有此道心也。其发也为食色,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食色之念乎。此由于血气成形,故有此人心也云尔。
非若互发之说或理发或气发而大本不一也。[13]
照上面的说法,“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这里的“其发也”乃是已发的形态。他说道心人心是已发,故随其发作而异名,这一点是合乎朱子思想的。此下栗谷开始反驳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但他的说法因“由于”而再次不清,他承认,朱子关于道心原于性命,人心生于形气的思想是从“既发”推本至根源,也就是从已发的状态推至未发的根源。朱子关于道心人心根源的思想与退溪有关四端七情根源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栗谷认为朱子这个说法与退溪的理发气发或理气互发的说法是不同的:
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无先后,无离合,不可谓互发也。[14]
这一段是栗谷此信的关键性表述,所以他自诩为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根据上面的分析,栗谷这里所说的“发之者”,是指已发而言,“所以发者”是指已发的欲念的内在根源。因此,按照退溪时代的讨论的用法,应该说,栗谷这个思想还是属于理发说,因为退溪所说的理发气发都首先是指内在的根源而言。虽然栗谷在这里还没有明确这个说法是专对人心道心而言或是包含四端七情而言,如果包含了对四端七情的看法,那就与高峰的看法一致,即四端七情都发于理、发于性。事实上栗谷确实是这样理解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栗谷所谓“气发”还可指已发与未发之间的过程状态,但都不是指发自于(作为根源的)气。从而,栗谷的“气发”与退溪的“气发”是不同的。
但人心道心,则或为形气,或为道义,其原虽一,而其流既岐,固不可不分两边说下矣。若四端七情,则有不然者,四端是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是四端之总会者也。一边安可与总会者,分两边相对乎?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说,分开拖引,则岂不至于辗转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15]
栗谷认为,道心人心,本原是一个,都是发自本性之源,它们的不同是流的分别。他认为,四端七情与道心人心不同,道心和人心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四端是七情的一部分,不能说作为部分的四端和作为整体的七情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一点也是与高峰一致的。他认为,道心和人心可以两边说,即从理气两个方向追溯其根源,而四端七情不是两个东西,只能从一个方向追溯其根源。
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16]
于是栗谷对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明确提出意见,认为退溪的“气发而理乘”的说法是可以的,但退溪以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认为四端不是气发而理乘之(而是理发而气随之),这是他不赞成的。栗谷主张七情、四端都是气发而理乘之的。这个说法就在形式上不仅与退溪不同,也与高峰不同了。但是应该提醒读者的是,退溪所说的“气发而理乘之”,与栗谷所说的“气发而理乘之”并不相同,退溪所说的气发是发自于形气,而栗谷所说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栗谷进一步说,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这是气,就是气发,而理乘载其上。由于栗谷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故把恻隐说成气,说成气发,这是与朱子和退溪不同的。他认为,气和理的这种动载关系是普遍的,不限于四端七情,整个天地之化都是如此。
前面我们分析栗谷的说法是一种理发说,但栗谷对“发”的理解与退溪不同,故他自己明确表示不赞成退溪的理发说或理发气随说:
若理发气随之说,则分明有先后矣,此岂非害理乎。天地之化,即吾心之发也,天地之化,若有理化者气化者,则吾心亦当有理发者气发者矣。天地既无理化气化之殊,则吾心安得有理发气发之异乎。若曰吾心异于天地之化,则非愚之所知也。(此段最可领悟处,于此未契,则恐无归一之期矣。)[17]
他认为,天地之化都是气化理乘,天地之化并没有理化气化之分,既然天地之化没有理化气化之分,人的心也必然没有理发气发之分。他在这里把天地之化只说成是气化理乘,并屡屡强调气发理乘,无形中遮掩了理作为气之主宰的意义,似显示出他理气论的偏向(虽然他也提到理是主宰和根柢)。
由以上可见,栗谷的思想是:第一,四端七情与道心人心不同,道心人心可以两边说其根源,四端七情不能两边说,只有一个根源;两边即所谓互发,即是二本。第二,即使朱子主张道心人心两边说,栗谷也不赞成,主张道心人心其实只是一个根源,朱子的说法是不得已。第三,四端是七情一部分,四端七情是一个根源而发。第四,栗谷的讨论的关注点已经从根源转向已发,用气发理乘为普遍命题贯通天地之化与人心之动,在哲学上即转向流行的现象世界。
且所谓发于理者,犹曰性发为情也。若曰理发气随,则是才发之初,气无干涉,而既发之后,乃随而发也,此岂理耶。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覆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
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18]
照这里的说法,退溪发于理的说法,是说性发为情,栗谷对此不持异议,也就说明他认可情发于性、“发自理”。而他关注的是“发为情”的过程机制。从而他讲的“发”,主要不是“发自”,而是“发为”。栗谷反对的是“理发气随”的说法,认为这样在理发与气随之间就有了时间的距离,理发在前,气随在后,这是他所反对的。他认为他自己所讲的“气发理乘”并不设定二者有时间的距离。
窍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虽圣人之心,未尝有无感而自动者也。必有感而动,而所感皆外物也。何以言之?感于父则孝动焉,感于君则忠动焉,感于兄则敬动焉。父也君也兄也者,岂是在中之理乎,天下安有无感而由中自发之情乎。特所感有正有邪,其动有过有不及,斯有善恶之分耳。今若以不待外感由中自发者为四端,则是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无兄而敬发矣。岂人之真情乎。今以恻隐言之,见孺子入井,然后此心乃发,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者乎?就令有之,不过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19]
栗谷强调,四端七情,人的一切心,都是感于外物而动的,没有能够无感而动的;感有正邪,动有过有不及,于是有了善恶之分。栗谷这个说法亦有未尽之处,这就是,心感外物而动,外物的感是必要的条件,但心的发动完全是以外物为条件吗?有没有内在的根据呢?朱子、退溪关于道心人心、四端七情的讨论,都重视心之所发的内在根源为何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把心之所发归结为外感。
夫人之性,有仁义礼智五者而已,五者之外,无他性。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而已,七者之外,无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别名,言七情则四端在其中矣,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对立名也。吾兄必欲立而比之,何耶。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七情之包四端,吾兄犹未见得乎。夫人之情,当喜而喜,临丧而哀,见所亲而慈爱,见理而欲穷之,见贤而欲齐之者,(已上喜哀爱欲四情)仁之端也。当怒而怒,当恶而恶者,(怒恶二情)义之端也。见尊贵而畏惧者,(惧情)礼之端也。当喜怒哀惧之际,知其所当喜所当怒所当哀所当惧,(此属是)又知其所不当喜所不当怒所不当哀所不当惧者,(此属非,此合七情而知其是非之情也)智之端也。善情之发,不可枚
举,大概如此。若以四端准于七情,则恻隐属爱,羞恶属恶,恭敬属惧,
是非属于知其当喜怒与否之情也,七情之外,更无四端矣。[20]
栗谷坚持,七情包括四端,四端作为善的情,是七情中的一部分,这是与道心人心的关系不同的。故道心人心可以做两边说,四端七情不可做两边说。如前所说,这是与高峰对退溪的异议是一致的,只是这里没有涉及气发理发的问题。
然则四端专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与人心道心之自分两
边者,岂不迥然不同乎。吾兄性有主理主气之说,虽似无害,恐是病根藏
于此中也。本然之性,则专言理而不及乎气矣。气质之性,则兼言气而包
理在其中。亦不可以主理主气之说,泛然分两边也。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
分两边,则不知者,岂不以为二性乎,且四端谓之主理,可也,七情谓之
主气则不可也。七情包理气而言,非主气也。人心道心,可作主理主气之
说,四端七情,则不可如此说,以四端在七情中,而七情兼理气故也。[21]
栗谷认为,道心人心与四端七情的关系不同,但四端七情可以与道心人心对应来看,四端对应于道心,七情则包括道心人心。他认为四端与七情的关系更类似于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因为四端专主理,七情包理气,本然之性专指理,而气质之性包括理和气,所以气质之性是包括本然之性在其中的。他对气质之性的理解合乎朱子之说。因此他反对四端主理、七情主气的说法,认为四端是七情的部分,整体包含部分,二者不能截然分两边说。四端主于理,则七情必然不能仅仅主气,必须包含主理的部分,故说七情兼理气。
其实,在此书之前,壬申年栗谷另一《答成浩原书》中已经提出:“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而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22]该书中栗谷还说:“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23]他承认七情皆发于理,道心人心皆发于性,惟发之过程中是否被气所掩,而分别成为善恶。退溪所说的理发,也是指发于理,发于性,可见栗谷后来否定理发说,只讲气发说,对他自己也是不合理的。
在退溪、高峰的辩论中,四端七情的兼理气问题,本来是与理发气发问题不同的讨论。但在二人的论辩中,在一定程度上被混同了。退溪、高峰理发气发主要是讨论四七的内在根源,兼理气的问题则是讨论现实的情感意念。高峰认为,一切现实的情感既不仅仅是理,也不仅仅是气,而是兼乎理气的。他说:“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24退溪也是如此,他说“理气合而为心”,又说:“二者皆不外乎理气,四端非无气,七
情非无理。”[25]其实在朱子哲学中,已发之情,不必再用理气来加分析,也就不会有气发理乘的讲法。退溪关于主于理、主于气的说法也都是指已发而言。由于他们不仅以理气来说明四端七情之所发的根源,也用理气来直接说明作为已发的四端七情本身,这是导致栗谷把四七理发气发的讨论重点从未发滑转向已发的重要原因。不过,由于朱子思想中从未对情本身做过理气分析,也未说过情即是气,所以韩国性理学对四端七情以及对整个情加以理气的分析,乃至出现各种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朱子学自身讨论的一种深入。
三
下面我们以《栗谷全书》卷十《栗谷答成浩原第二书》(即承委问)为主,对栗谷思想进一步加以分析。
理,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二者不能相离,既不能相离,则其发用一也。不可谓互有发用也。若曰互有发用,则是理发用时,气或有所不及,气发用时,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则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其错不小矣。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26]
栗谷反对理气互发说,认为讲理气互发必然导致理气有先后,理气有离合,动静有端,阴阳有始,而陷于错误。在他看来,情皆出于本然之性,这里的“出于”实等同于退溪所说的“发于”,发于本性而不受形气遮掩的四端之情,属之于理;发于本性而被形气遮掩的情,属之于气。这应该是指朱子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朱子不得已的讲法。还可以看到,就他所说的属之气的情,“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其说法实同于退溪所说的理发而气掩之。用退溪学的语言来分疏,他实际认为四端七情都是理发,即发自于理,这与高峰一致。从退溪、高峰论辩的意义上看,栗谷实际上认可四端是理发而直遂,四端以外的其他情感则是理发而气掩:
理之本然者,固是纯善,而乘气发用,善恶斯分。徒见其乘气发用有善有恶,而不知理之本然,则是不识大本也。徒见其理之本然,而不知其乘气发用,或流而为恶,则认贼为子矣。是故,圣人有忧焉,乃以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使人存养而充广之;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使人审其过不及而节制之,节制之者,道心之所为也。夫形色,天性也,人心,亦岂不善乎。由其有过有不及而流于恶耳。若能充广道心,节制人心,使形色各循其则,则动静云为,莫非性命之本然矣。[27]
这一段又说到道心人心。栗谷认为,理之本然即是性,性发为情的过程就是理乘气发用的过程,情在发作过程中能直接遂成其性命之理,这样的情就被看作是道心。情在发作过程中被形气所掩蔽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理,这样的情就被看作是人心。从退高之辩的角度看,这里所说仍然是理发直遂为道心,理发气掩则为人心。
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为乎。圣贤之千言万言,只使人捡束其气,使复其气之本然而已。气之本然者,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则本善之理,无少掩蔽。此孟子养气之论,所以有功于圣门也,若非气发理乘一途,而理亦别有作用,则不可谓理无为也。孔子何以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乎?如是看破,则气发理乘一途,明白坦然。而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亦得交通而各极其趣。试细玩详思,勿以其人之浅浅而辄轻其言也。[28]
栗谷在这里明确把其主张概括为“气发理乘”,观其所说,气发理乘具有二义:第一个意义是普遍的理气观意义,即天地之化,“气发”指天地间阴阳动静的运动,是流行之已然;“理乘”指理搭载在气上随气而动静。可见,在一般理气观的意义上,气发理乘是就存在的总体而言,即就流行之统体而言,故气发理乘不是仅仅指气,也不是仅仅指理,而是理气合一的实存流行状态。气发理乘在理气观上是指现实的、整合的存在,不是分析的概念,由此可见理气合一思想实为其根本思想。他也指出,理具有动静的所以然意义。应该说,这些提法在朱子思想中都有根据。第二个意义特指人心,即吾心之发,所以在心性论的意义上,栗谷的“气发”不是指根于气而发出,而是指心气的发动本身。他指出,讲气发理乘,并不意味着气先于理,是因为气是能动的实体,理则是无为无形的,故不得不先说气再说理。可见他在内心有着一种以能动实体为第一性的观念。
他进一步把这个思想称作“气发理乘一途”之说:
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与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通贯。吾兄尚于此处未透,故犹于退溪理气互发,内出外感,先有两个意思之说,未能尽舍,而反欲援退溪此说,附于珥说也。别幅议论颇详,犹恐兄未能涣然释然也。[29]
他认为,用气发理乘一途说,可以贯通于朱子的道心人心或原于性命或生于形气的说法,也可以贯通于朱子关于太极动静的人马比喻。他甚至认为,气发理乘是根本之论,朱子的说法则是沿流之论: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沿流之论也。今兄曰:其未发也,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此则合于鄙见矣。但谓性情之间,元有理气两物,各自出来,则此非但言语之失,实是所见差误也。又曰就一途取其重而言,此则又合于鄙见。一书之内,乍合乍离,此虽所见之不的,亦将信将疑,而将有觉悟之机也。今若知气发理乘与人信马足,马从人意,滚为一说,则同归于一,又何疑哉。道心原于性命,而发者气也,则谓之理发不可也。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焉。[30]
道心原于性命,朱子的这一观点栗谷并不反对,而他的正面观点是“发者气也,则谓之理发不可也”,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栗谷所用的理发气发,其发字不是指发自,而是指发动,因此退溪所说的气发是指根于气而发,或发自于气,是指情意思欲发动的根源;而栗谷所用的发是指发动,是运动作用的层面,不是根源的层面。因此在栗谷看来,气是现实化的力量,发动的只能是气,不能是理,因为理无为无形,理是不能活动的,于是只能说气发,不能说理发,理是不能发动、运动的。如果用已发未发的分别来看,退溪说的理发气发主要是指已发的根源,而栗谷所说的气发则是指已发的形态而言。退溪关注的是内在根源,而栗谷关注的是发动作用,二者的层次不同。前者的重点在“根源性”,后者的重点在“现实化”,退溪、栗谷都用“气发”,但二者的用法根本不同。栗谷说的发者气也,就是指已发的、发动的层面而言,因此他根本否定理发的说法。他在这里所说的人心道心都是气发,而这种说法是朱子思想中所没有的。另外,栗谷理气论、心性情论中对气的某种偏重,应与明代儒学理气论、心性论中气的因素越来越受重视有关。①
气顺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气发,而气听命于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主气言。气之听命与否,皆气之所为也,理则无为也,不可谓互有发用也。但圣人形气,无非听命于理,而人心亦道心,则当别作议论,不可滚为一说也。且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发而性不发之理,则岂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非当初有理气二苗脉也。立言晓人,不得已如此。而学者之误见与否,亦非朱子所预料也。如是观之,则气发理乘与或原或生之说,果相违忤乎?[31]
所以,栗谷讲的气发是“原于理”的,用退溪的话来说这个气发是发于理的。一切意识情感都为气发,但都是发自于本然之理。由于在栗谷思想中,认为从发自本性到发作为现实意识情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气参与其中,气是现实性的力量,没有气的参与,根于本性的“发”就不能真正发作为现实的意识情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分化为两种发作的方向,一种是气顺乎本然之理,一种是气变乎本然之理,前者就发作为道心,后者则发作为人心。前者气听命于理,后者气不听命于理。栗谷把气听命于理视作主于理,把气不听命于理视作主于气;他认为朱子讲的或生于性命或生于形气,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而不应从两种根源来理解(因为在栗谷看来只有一种根源即性理)。栗谷认为,无论前者后者,都与所谓理气互发没有关系。由于四端是七情的一部分的观点和四端七情皆发自性理的观点是高峰在退高之辩中所持的观点,故栗谷的中心观点无非有二:一是认可道心人心皆出自性理,二是强调已发的道心人心(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后者是栗谷思想的重点,表现出栗谷重视已发、流行的世界的倾向。至于栗谷在这里主张气之听命与否,皆气之所为也,理则无为也,已违离了朱子道心宰制人心、人心听命道心的思想,一切归为气之所为,一切功夫只落到检束其气上,这些与朱子重视检束此心的思想也是不同的。①至于栗谷这里所说的“心是气”,把心只理解为已发之气,就更与朱子思想不同了,而有近于朱子所批评的“心为已发”说。而且,这与他自己说的七情兼理气也不一致,在栗谷,心之发当为气发而理乘,七情也是气发而理乘,他既说“七情谓之主气则不可”,又怎么能说心是气呢?
栗谷的这一说法也接近于王阳明对性气的说法。阳明曾说:“孟子性善是从本源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看始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32我曾指出,孟子所说的四端,朱子哲学称为情,而在阳明看来是气,照阳明的看法,似乎只要是“发”,就属于“气”。如果作用层次上的意识情感活动都可称为气,那么,就会导致“心即气”的说法,而这与“心即理”显然有冲突。[33]事实上,正是在明代阳明学中有很多“心即气”的说法。
其实,栗谷的这种思想,就气顺或气掩而言,用退溪的讲法,实质是理发而气顺之或理发而气掩之。而这种理发气顺的意思,和栗谷口头上所反对的退溪的理发气随说是一致的。又由于栗谷不反对退溪的气发而理乘的说法,而且将退溪专指七情的这一说法扩大到四端,这样一来,在形式上,栗谷的真正立场和退溪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并不全部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他其实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个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此即所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由此可见,一般认为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退溪“理发气随”,其实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做细致的思想分析,这是本文希望强调的一点。①
朱子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固然构成了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和体系框架,但朱子对这些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并不都是究极性的,这一体系所包含的问题也没有被朱子个人所穷尽。因此后世朱子学对朱子的发挥、修正、扩展、深化都是朱子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这方面,朝鲜时代的朱子学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和贡献。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及展望
〔韩〕崔英辰
一、序论
如我们所知,朱子学自14世纪末传入朝鲜以后,逐步成为主导朝鲜社会发展的治国理念。建立朝鲜的主体是士大夫(即官僚兼学者),他们主导了“易姓革命”并形成了超越王权的庞大权力集团。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把重点放在了权力的分散和抑制权力的过分集中上,力求通过政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来实现以民为本的民主社会。朝鲜社会推动政策实施的主体其实就是士大夫[1],他们徘徊在辅佐和遏制王权的立场之间,创建了抑制王权的制度体系。[2]因此士大夫渐渐成了左右朝鲜王权更替的主导力量。[3]
作为官僚兼政治家的朝鲜士大夫,他们掌握实权并能参与政策的实施,所以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此外朝鲜学派和政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学术论争往往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4]朝鲜社会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学术论争,并在数百年以来持续发展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与朝鲜社会的特殊性有着很深的关联。
众所周知,朝鲜的性理学是在三次比较集中而又持续的论争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它们分别是:16世纪的“四端七情论争”、18世纪的“湖洛论争”以及19世纪的“心说论争”。四端七情论争是以“情”为中心,湖洛论争是以“性”和“未发心”为中心,心说论争则是以“心”为主题来展开。通过这三次论争,朝鲜性理学者对心性情的研究更加细致透彻,同时也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问题点。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理念,并以此确立且形成了有别于中国朱子学的韩国性理学。如此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在日本和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在三大论争中,研究成果最多的应该是“四端七情论争”。最近,对“湖洛论争”的研究也陆续展开,而对“心说论争”的研究却还处于空白状态。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心说论争”更是陌生。而它与“四端七情”和“湖洛论争”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进一步探究朝鲜性理学史的深入发展,“心说论争”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难题。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
寒洲李震相(1818~1886)在43岁时撰写的《心即理说》成了引发岭南学派内部论辩的导火索,接着也引发了与畿湖学派的激烈论辩。在《心即理说》中,寒洲批判“心是气”,强烈主张“心即理”。
朝鲜性理学从16世纪退栗时代开始,就试图用理气论来解释心和其他世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例如湖洛论争讨论“未发论”的核心问题时,提出构成未发之心的气是“湛然纯善”还是“清浊美恶”,纯善的本然之心是否是“理气同实”[5],这都是不同于朱子“中和说”的部分。而从理气论的角度去回答“心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会有“心合理气”“心即理”和“心即气”三种不同的答案。如我们所知,朱子学中把心规定为“理+气”,退溪也是主张“心合理气”。但是自栗谷主张“心是气”[6]之后,这便成了畿湖学派的宗旨。而寒洲认为“心是气”这一主张歪曲了由“孔子-孟子-朱子-退溪”所传承下来的儒学的一贯宗旨。这一点通过寒洲“论心莫善于心即理,莫不善于心即气”可以得到很好的证实。
为了批判“心是气”,寒洲提出了“心即理”,并认为自己的“心即理”才是真正传承并发展了退溪的理论。[7]但“心即理”类同于被退溪划为异端的阳明学的理论,所以不仅在岭南学派内部受到了极大的批判,在畿湖学派内部也是如此。
二、1902年~1990年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畿湖学派的其中一支是华西学派,张志渊的《朝鲜儒教的渊源》[8]一书对这一学派的心说进行了整理。书中记述了柳重教(1832~1893)和金平默(1819~1891)的观点,并简单叙述了他们对李恒老(1792~1868)心说定论的论争。李恒老是二人的恩师,柳重教在《论调补华西先生心说》中首先提出了对心说的异议,后金平默针对柳重教的论旨作《华西先生心说本义》,对恩师心说的意义进行了重申。张志渊以“京嘉两派的分裂”为题,将其分裂的过程进行了简单论述。这里的“京”是指以首尔为势力范围的洛论派系学者[9],“嘉”是指李恒老居住在“嘉陵”,即现在嘉平一带的门生。[10]由于洛论学者的学脉师承梅山洪直弼,所以这场论辩也叫作“华梅是非”。
这之后玄相允(1893~?)也对此论辩做了记载。他在《朝鲜儒学史》[11]“柳重教”一条中,对与金平默明德主理主气的论争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述。之后,裴宗镐在《韩国儒学史》[12]一书中以“明德主理主气论辩”为题,对李恒老的门人、洪直弼和吴熙常的门人,以及其再传门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做了详细叙述,他评价说“这场论争比湖洛论争更加激烈”。这三本概论书中虽然都使用了“心说”这一单词,但是却没有提及“心说论争”这一词语。
“心说论争”这一词语最开始是1983年吴锡源在《关于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研究》[13]中使用的。[14]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心说”这一词语已经包含在了华西学派内,所以使用了“心说论争”这一词语。吴锡源在论文中首先考察了李恒老的心说,然后详细考察了柳重教、金平默、崔益铉(1833~1906)对于明德的看法,最后指出了“心说论争”的特征和意义。吴锡源的论文发表之后,间或有关于朝鲜后期“心说论争”的论文出现,逐渐扩大了心说的研究范围。
吴锡源论文发表后虽然出现了有关李恒老及其学派的研究[15],但学界对于“心说论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心[16]。这是因为学界的研究方向大多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再者就以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为重点,关于心说论争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仅有两篇。
一篇是宋锡准的《对艮斋性师心第说和俛宇心即理说的考察》,1998年刊登于《艮斋学论丛》第二辑上,对艮斋的性师心第说和俛宇的心即理说进行了比较性考察。李炯性则着重考察了郭钟锡的老师李震相,对他的心即理说和以心使心论中心的主宰性进行了考察。17]以心使心虽然是首次在性理学心性论领域里被提及,但其实它是李震相心主宰性的一环。[18]
另一篇是朴洪植的《明德理气论辨》(《东洋哲学研究》第20辑,东洋哲学研究会,1999),文中指出明德理气论这一问题来源于明德主理主气的讨论,详细记述了参与此次讨论的人物及其观点,明德说以“主理”“主气”为分歧展开,“主气说”以洪直弼、任宪晦、柳重教为主,“主气说”以奇正镇、李恒老、崔益铉、李震相为主,并列举了他们的原文。
三、2000年~2009年研究领域的扩大和主要论文
近现代的性理学者虽然对性理学研究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2000年以来对性理学思想的关心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其中关于心说论辩的博士论文如下:
朴鹤来:《芦沙奇正镇的哲学思想研究》,高丽大学,2001年2月。
李炯性:《寒洲李震相的性理学研究》,成均馆大学,2001年2月。
姜弼善:《华西李恒老的哲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2002年8月。
朴性淳:《华西李恒老心主理说与斥邪论的研究——关于朝鲜后期畿湖老论洛学派心说的传承》,高丽大学,2003年8月。
李相下:《寒洲李震相性理学说的立论根据》,高丽大学,2003年12月。
李宗雨:《对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心性论争研究》,成均馆大学,2004年8月。
金勤皓:《华西李恒老的理学心论研究》,高丽大学,2008年2月。
李美林:《华西李恒老的华夷论研究》,成均馆大学,2009年2月。
以上论文中李炯性、李相下、李宗雨的论文是关于寒洲学派的,朴鹤来的论文是关于芦沙的,剩下的都是关于华西学派的。
(一)以寒洲学派为主的研究
1.关于寒洲的研究
李炯性:《寒洲李震相心即理说的含义》,《阳明学》,韩国阳明学会,2002年8月。
李宗雨:《对李震相心即理说渊源的考察》,《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03年9月。
朴祥里:《对寒洲李震相心即理说的研究》,《儒教思想研究》,韩国儒教学会,2004年8月。
李相下:《寒洲李震相心说的性质——以与岭南学派基本的心合理气说·王阳明的心即理说的差异为中心》,《东洋汉文学研究》第19辑,东洋汉文学会,2004年6月。
李炯性:《从修养论的层面来考察寒洲思想的心说》,《韩国思想和文化》第36辑,韩国思想文化学会,2007年1月。
金洛真:《以知觉说为中心来看寒洲李震相的性理学——以心即理说成立的历史背景为中心》,《东洋古典研究》第36辑,东洋古典学会,2004年9月。
权相佑,《19世纪岭南退溪学的定论与创新二重奏——从李万寅与张福枢的立场来看李震相的“心即理说”》,《南冥学研究》第28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12月。
2.对寒洲学派与艮斋学派论争的研究
李宗雨:《对寒洲与艮斋心说论争的研究——以“心即理说”和“李氏心即理说条辨”为中心》,《韩国哲学论集》第10辑,韩国哲学史研究会,2001年12月。
李宗雨:《对朱熹晚年定说论争的研究——以李震相学派和田愚学派的论争为中心》,《退溪学报》第114辑,退溪学研究院,2003年12月。
李宗雨:《李震相学派和田愚学派的知觉说论争》,《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04年3月。
李宗雨:《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对主宰论的论争及其评价》,《东洋哲学》第22辑,韩国东洋哲学会,2004年12月。
李宗雨:《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对义理实践的论争》,《韩国哲学论集》第15辑,韩国哲学史研究会,2004年9月。
李宗雨:《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对心统性情的论争及其意义》,《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05年5月。
林宗镇:《晚求李钟杞性理学的立场的考察——以与寒洲学派的论辩为中心》,《退溪学与儒教文化》第43辑,退溪研究所,2008年8月。
3.对寒洲弟子郭钟锡的研究
洪元植:《俛宇郭钟锡的明德说——以李承熙·许愈·金镇祜的论争为中心》,《南冥学研究》第27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6月。
洪元植:《俛宇郭钟锡的性理说——以对寒洲性理说的继承为中心》,《南冥学研究》第27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6月。
李相下:《俛宇郭钟锡的性理说——对寒洲性理学的继承与传播》,《南冥学研究》第28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12月。
4.其他
崔英辰:《对18~19世纪朝鲜性理学的心学化倾向的考察》,《韩国民族文化》第33辑,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2009年。
以上这些论文可以分为关于寒洲心说的论文,关于寒洲学派与艮斋学派论辩的论文,关于寒洲的弟子郭钟锡的论文,而崔英辰的论文则将寒洲的心即理说与湖洛论争的代表性学者李谏的“心性一致”说相联系,从朱子心学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分析、再解释。
除此之外,定斋柳致明(1777~1861)学派对寒洲学派[19]批判性考察的论文[20]、韩国阳明学者霞谷郑齐斗(1649~1736)与李震相的心性论的比较研究论文[21]也在学界发表,扩大了对李震相思想的理解范围。
(二)以寒洲学派为主的研究
李相益:《寒洲李震相的主理论及其批判》,《温知论丛》第27辑,温知学会,2011年1月。
尹丝淳:《寒洲李震相性理学式的心即理说》,《孔子学》第20辑,韩国孔子学会,2011年5月。
洪元植:《19世纪“洛上”退溪学派与“洛中”寒洲学派的分立以及性理学论争——以韩溪李承熙的“条辨”为中心》,《儒家思想文化史》第39辑,韩国儒教学会,2010年3月。
崔英辰:《19~20世纪朝鲜性理学“心即理”与“心是气”的冲突:以艮斋和重斋对寒洲“心即理”的论辩为中心》,《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13年2月。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尹丝淳在论文中的主张:
细细体会李震相以主宰为基础的心即理说就会发现,他理论体系中的“心的主宰”就是“理的妙用”。心是意识作用,其作用就是理性的思考和
担心的情绪。也可以把他的意识作用说成是形式上“主张和宰制”,但是主宰心的体是理,也即天,这种替天主宰的方式是不是可以作用于其他地方,是不是必须只能起到这一种作用,都是需要作进一步考察的。另外从根本上说“理的主宰”本身与气的作用性质就是“名目名分”的差异,按照李震相的理论其主宰作用免不了被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规定”。
尹丝淳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李震相的心即理说,扩大了其范围。崔英辰的论文在2012年第四次国际汉学会议中儒学分科进行了初稿的发表,后经补完收录在了2013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发行的《东亚视域中的儒学:传统的解释》中。有趣的是,此书中收录了14篇论文,其中关于韩国儒学的论文就有8篇之多。论文中崔英辰考察了艮斋对寒洲心即理说的批判以及寒洲的再传弟子金榥对此的回应,并分析了他对寒洲的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三)以华西学派为主的研究
朴性淳:《毅庵柳麟锡对华西心说的传承样相》,《东方学》第27辑,东洋古典研究所,2013年5月。
金勤皓:《试论华西李恒老性理说的心学特征》,《栗谷思想研究》第26辑,栗谷学会,2013年6月。
金勤皓:《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展开过程与哲学的问题意识》,《栗谷思想研究》第27辑,栗谷学会,2013年12月。
杨祖汉:《韩国朝鲜后期儒学的心论:以华西学派为中心》,《东亚视域中的儒学:传统的解释》,2013年10月。
其中杨祖汉的论文是关于华西与其弟子省斋柳重教之间展开的心的论辩,省斋批判华西的“以理言”“以气言”,并主张将心和性严格按照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区分,将心归属于气,杨祖汉认为这是对华西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四)以艮斋学派为主的研究
艮斋学会在学术会议上考察了艮斋学派与其他学派理论的同异之处,将这些论文集结成特辑发行在《艮斋学论丛》第10辑:
林月惠:《艮斋学派与俛宇学派在思想上的同异及特征——以艮斋与俛宇的心说论争为中心》。
蔡家和:《艮斋学派与寒洲学派的思想同异及特征——田艮斋“心是气”与李寒洲“心即理”的差异比较》。
李宗雨:《艮斋学派与华西学派的思想同异及特征》。
除此之外,艮斋学派的相关研究还有:
林玉均:《艮斋田愚与醒庵李喆荣性理思想的同异和特征》,《艮斋学论丛》第14辑,艮斋学会,2012年8月。
张淑必:《艮斋与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焦点与意义》,《栗谷思想研究》第27辑,栗谷学会,2013年12月。
(五)对奇正镇(1798~1879)学派心说的研究
朴鹤来:《奇正镇的心论与明德说》,《韩国思想史学》第16辑,韩国思想史学会,2001年6月。
朴鹤来:《畿湖学界围绕奇正镇“纳凉私议”的论争》,《民族文化研究》第36辑,民族文化研究院,2010年6月。
金勤皓:《从溪南崔琡民的“明德之学”看心论》,《南冥学研究》第30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12年12月。
朴鹤来:《对芦沙奇正镇学派心说的考察》,《儒学思想文化研究》第43辑,韩国儒教学会,2011年3月。
芦沙学派认为心是理气之合,并强调精爽之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心本善”确认了心与性都是善的,从修养和实践的层面上认为心的根本体系可以实现善。朴鹤来为了阐明心说论争在道德(教育)论上的意义,对韩末性理学界的心说论争进行了考察[22],试图分析“心说论争‘以如何实现已知的人类道德本性为出发点,对心从实践层面的探讨'”。
朝鲜后期开始探讨华西学派内部的“心说论争”,其主要主旨虽然是明德主理主气,但同时也是通过认识真正的人类主体来确立人类学。
(六)其他
金景浩:《栗谷学派的心是气与其哲学的问题意识》,《栗谷思想研究》第27辑,栗谷学会,2013年。
金勤皓:《从19世纪心论的主题来看栗谷学的样相——以任宪晦、宋秉璇、李恒老、奇正镇等为中心》,《栗谷思想研究》第28辑,栗谷学会,2014年。
金景浩:《栗谷学派的心学与实学》,《韩国实学思想研究》第28辑,韩国实学学会,2014年。
以上论文都是对栗谷学心说论争焦点的阐释。
四、“心说论争”研究的新探索
韩国朱子学的三大论争是始于对心性情理气论的规定,众所周知,朱子认为四端与七情都是情感,并没有系统地对心进行理气论的规定。因此,韩国朱子学者们试图用理气论的概念来定义人类的心性,在这个理论整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的理论创新。
未来的研究课题如下:
韩国朱子三大论争之间的关系研究
目前为止对于各个论争的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三大论争之间的关系性研究,以及理论发展的研究则有很多不足。[23]
韩中日儒学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
抽出中日关于心说论争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可以确认韩国儒学的正统性,同时可以阐明东亚儒学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与其他学派心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与阳明学派及实学派的比较研究确立心说论争理论的特殊性。
从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立场上进行研究
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心论比较来阐明心说论争理论的特殊性。
有必要引入西方的心理学(特别是道德心理学)、脑科学等对人类心脏研究的最新现代科研成果对心说论争理论进行检证。[24](作者单位:韩国成均馆大学)
——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陈来
朱子心性论对于性情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1],以性为情的内在根据,情是性的外发表现。《孟子》曾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朱子的解释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2]《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子解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3]朱子哲学中的“情”有两种用法,一指四端(《孟子集注》说),一指七情(《中庸章句》说)。四端是道德情感,纯善无恶,七情则泛指一切情感活动,有善有恶。朱子以“四端”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这合于“性发为情,情根于性”的基本原则。而如果说喜怒哀乐等“七情”有善恶邪正,那就碰到一个问题,即七情中发而不善的情感是否也是发于仁义礼智的本性?如果说不善之情也是发于全善之性,这显然是有矛盾的。而且,朱子从未肯定七情中不善者不是发于本性。这是朱子学中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
朱子哲学曾提出,人是由理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退溪根据这一看法,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发自人的形体(气)。退溪“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这一命题的提出,主张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使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李退溪曾与奇大升(高峰)反复论辩,成为朝鲜朝性理学史的一大事件。奇大升反对“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的提法,他认为七情泛指人的一切情感,四端只是七情中发而中节的一部分,因而四端作为部分应与作为全体的七情共同发自同一根源,即皆发于仁义礼智之性。奇大升这个说法以朱子《中庸章句》说为据,并可在朱子学体系内找到较多支持,但无法解决朱子心性论自身未解决的问题。在李退溪看来,以为“七情”有两种用法,一种同于奇说,即“以混沦言之”,在这个意义上,四端包容在七情之内,一种则以七情与四端相对而言,以七情为四端以外的其他情感,包括反映人的生理需要的各种情感以及非道德情感等。退溪正是在后一种用法的意义上,认为七情不是发于性,而是发于气。
退溪的说法虽在朱子哲学中所能找到的根据较少,但显然力图在朱子基础上有所发展,使朱子学体系更加完备。同时,他认为四七分理气并不是说四端仅仅是理,七情仅仅是气,四端与七情都是兼乎理气的。他说“二者皆不外乎理气”[4],“四端非无气”,“七情非无理”[5],认为四端七情作为现实情感无不兼乎理气,因为心是理气之合,情也是理气之合,但二者“虽同是情,不无所从来之异”[6],二者作为现实意识或情感虽皆兼乎理气,但就二者所发的初始根源说,四端发自性理,七情发于形气。他说:
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乎气,四端是也。
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乎理,七情是也。[7]退溪认为四端与七情虽然都兼乎理气,但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从性理发出而气顺随加入而成的是四端,从形气发出而理随之乘驭而成的是七情,所谓四七分理气,并不是说四端纯是理,七情纯是气,只是说四端发于理、主于理,七情发于气、主于气。退溪的这一思想,把人的情感区分为反映或适应生理需要的自然情感(七情)和反映社会价值的道德感情(四端),并认为二者形成的根据与方式不同,前者根于人的生理躯体,后者来源于人的道德本性。气随、理乘则指四七构成的方式和发用的机制,这些思想较之以前“理学”的处理更进了一步。
表面上看来,相对于奇高峰的主张,李退溪四七分理气的思想在朱子思想材料中的根据较少,但在实质上,可以认为是对朱子处理道心人心思路的一个扩展。按照朱子思想,人的意识被区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指道德意识,人心则指感性欲念。朱子认为“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8],这也就是认为道心理之发,人心气之发。李退溪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思想应该说是朱子道心人心说应用于情感分析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关于四七分理气的问题,其直接意义是区分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不同来源与根据,并不意味着理发一定为善或气发一定为恶。根源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善恶的分别还决定于人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努力,改善四七的构成方式和发用机制。李退溪说:
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而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9]
所以,四端虽发于理而无不善,但并非一切理发者皆为善,理发的过程中如果因气的冲击而不能保持原来的方向,则流于不善。七情发于气,如果气发的过程受到理的控制与有力引导,则可以为善;如果理不能在气发的过程中及时控制引导,则流为不善。可见善恶之间的关键还在于发作过程中理气的相为胜负。这里说的理气胜负实际上就是指道德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欲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发也,理显而气顺则善,气掩而理隐则恶”[10],只有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使理性能驾驭、控制、引导感性即“以理驭气”11,思维情感才能呈现为善。这些讨论是在四七内在根源的问题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的理发或气发的过程和机制。
可见退溪高峰的理发气发之辩,主要关注的是四七“发于”何处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又涉及了四七“发用”的过程和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退溪和高峰的四七辩论中,所谓理发气发的“发”的讨论包含二义,一个是“发于”,如情发于性;另一个是“发用”,如性发为情。“情发于性”和“性发为情”,这两个命题在表达性情的体用关系上是一致的,而在表达的方向顺序上不同,其中“发”所连接的介词不同,从而造成了有关理发气发讨论的不同意义。在退溪、高峰的讨论中,“发于”的问题是主要的。
朝鲜时代儒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①,但始终没有以四端七情普遍对举成为讨论课题,更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一点上,朝鲜时代性理学是有其贡献的。
二
一般认为,栗谷的思想接近朱子而与退溪的立场相反,集中体现在有关四端七情的讨论。其实,栗谷更多的讨论是围绕道心人心之根源与发动的讨论,其观点和朱子多有不同。而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下面,我们以《栗谷全书》卷十《栗谷答成浩原第一书(壬申)》(数日来道况如何)为基本资料,来梳理、分析栗谷的思想。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复礼,欲穷理,欲忠信,欲孝于其亲,欲忠于其君,欲正家,欲敬兄,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固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揜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渴欲饮,痒欲搔,目欲色,耳欲声,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之人心。其原虽本乎天性,而其发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12]
这一段是解释和说明道心人心的。栗谷从道心人心的界定开始而不是从四端七情的说明开始,表明他首先针对朱子之说。他从《乐记》的感动说开始,首先认为一切欲念的产生都是感动者引起的,而感动者都是形气。道德的欲念是道心,自然的欲望是人心。他认为,就欲念的发生而言,道心出于仁义礼智,而且没有受到形气的遮蔽;人心也是本源于本性,但其发生由乎耳目形气之私。照他的说法,道心、人心都应在本源上出自仁义礼智的本性,只是道心在发生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形气的遮蔽,而人心在发生的过程中受了形气的影响而异变了。这个说法,如果用退溪、高峰的理发气发的说法,在内在根源的意义上,应当属于道心人心皆理发说,就是道心人心都“发自”于理的本性。这就与朱子不同,因为朱子《中庸章句序》主张道心原于性命之理,人心生于形气之私。①
这里还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栗谷所用的“发”字,如“其发也”是指发自,还是发出、发为?是表达未发的根源,还是已发的过程和形态?②
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鞲,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若来书所谓理气互发,则是理气二物,各为根柢于方寸之中。未发之时,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发则为道心,气发则为人心矣。然则吾心有二本矣,岂不大错乎。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吾兄何从而得此理气互发之说乎。其所谓或原或生者,见其既发而立论矣。其发也为理义,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理义之心乎。此由于性命在心,故有此道心也。其发也为食色,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食色之念乎。此由于血气成形,故有此人心也云尔。
非若互发之说或理发或气发而大本不一也。[13]
照上面的说法,“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这里的“其发也”乃是已发的形态。他说道心人心是已发,故随其发作而异名,这一点是合乎朱子思想的。此下栗谷开始反驳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但他的说法因“由于”而再次不清,他承认,朱子关于道心原于性命,人心生于形气的思想是从“既发”推本至根源,也就是从已发的状态推至未发的根源。朱子关于道心人心根源的思想与退溪有关四端七情根源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栗谷认为朱子这个说法与退溪的理发气发或理气互发的说法是不同的:
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无先后,无离合,不可谓互发也。[14]
这一段是栗谷此信的关键性表述,所以他自诩为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根据上面的分析,栗谷这里所说的“发之者”,是指已发而言,“所以发者”是指已发的欲念的内在根源。因此,按照退溪时代的讨论的用法,应该说,栗谷这个思想还是属于理发说,因为退溪所说的理发气发都首先是指内在的根源而言。虽然栗谷在这里还没有明确这个说法是专对人心道心而言或是包含四端七情而言,如果包含了对四端七情的看法,那就与高峰的看法一致,即四端七情都发于理、发于性。事实上栗谷确实是这样理解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栗谷所谓“气发”还可指已发与未发之间的过程状态,但都不是指发自于(作为根源的)气。从而,栗谷的“气发”与退溪的“气发”是不同的。
但人心道心,则或为形气,或为道义,其原虽一,而其流既岐,固不可不分两边说下矣。若四端七情,则有不然者,四端是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是四端之总会者也。一边安可与总会者,分两边相对乎?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说,分开拖引,则岂不至于辗转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15]
栗谷认为,道心人心,本原是一个,都是发自本性之源,它们的不同是流的分别。他认为,四端七情与道心人心不同,道心和人心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四端是七情的一部分,不能说作为部分的四端和作为整体的七情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一点也是与高峰一致的。他认为,道心和人心可以两边说,即从理气两个方向追溯其根源,而四端七情不是两个东西,只能从一个方向追溯其根源。
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16]
于是栗谷对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明确提出意见,认为退溪的“气发而理乘”的说法是可以的,但退溪以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认为四端不是气发而理乘之(而是理发而气随之),这是他不赞成的。栗谷主张七情、四端都是气发而理乘之的。这个说法就在形式上不仅与退溪不同,也与高峰不同了。但是应该提醒读者的是,退溪所说的“气发而理乘之”,与栗谷所说的“气发而理乘之”并不相同,退溪所说的气发是发自于形气,而栗谷所说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栗谷进一步说,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这是气,就是气发,而理乘载其上。由于栗谷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故把恻隐说成气,说成气发,这是与朱子和退溪不同的。他认为,气和理的这种动载关系是普遍的,不限于四端七情,整个天地之化都是如此。
前面我们分析栗谷的说法是一种理发说,但栗谷对“发”的理解与退溪不同,故他自己明确表示不赞成退溪的理发说或理发气随说:
若理发气随之说,则分明有先后矣,此岂非害理乎。天地之化,即吾心之发也,天地之化,若有理化者气化者,则吾心亦当有理发者气发者矣。天地既无理化气化之殊,则吾心安得有理发气发之异乎。若曰吾心异于天地之化,则非愚之所知也。(此段最可领悟处,于此未契,则恐无归一之期矣。)[17]
他认为,天地之化都是气化理乘,天地之化并没有理化气化之分,既然天地之化没有理化气化之分,人的心也必然没有理发气发之分。他在这里把天地之化只说成是气化理乘,并屡屡强调气发理乘,无形中遮掩了理作为气之主宰的意义,似显示出他理气论的偏向(虽然他也提到理是主宰和根柢)。
由以上可见,栗谷的思想是:第一,四端七情与道心人心不同,道心人心可以两边说其根源,四端七情不能两边说,只有一个根源;两边即所谓互发,即是二本。第二,即使朱子主张道心人心两边说,栗谷也不赞成,主张道心人心其实只是一个根源,朱子的说法是不得已。第三,四端是七情一部分,四端七情是一个根源而发。第四,栗谷的讨论的关注点已经从根源转向已发,用气发理乘为普遍命题贯通天地之化与人心之动,在哲学上即转向流行的现象世界。
且所谓发于理者,犹曰性发为情也。若曰理发气随,则是才发之初,气无干涉,而既发之后,乃随而发也,此岂理耶。退溪与奇明彦论四七之说,无虑万余言,明彦之论,则分明直截,势如破竹,退溪则辨说虽详,而义理不明,反覆咀嚼,卒无的实之滋味。明彦学识,岂敢冀于退溪乎,
只是有个才智,偶于此处见得到耳。[18]
照这里的说法,退溪发于理的说法,是说性发为情,栗谷对此不持异议,也就说明他认可情发于性、“发自理”。而他关注的是“发为情”的过程机制。从而他讲的“发”,主要不是“发自”,而是“发为”。栗谷反对的是“理发气随”的说法,认为这样在理发与气随之间就有了时间的距离,理发在前,气随在后,这是他所反对的。他认为他自己所讲的“气发理乘”并不设定二者有时间的距离。
窍详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做出许多葛藤,每读之,未尝不慨叹,以为正见之一累也。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虽圣人之心,未尝有无感而自动者也。必有感而动,而所感皆外物也。何以言之?感于父则孝动焉,感于君则忠动焉,感于兄则敬动焉。父也君也兄也者,岂是在中之理乎,天下安有无感而由中自发之情乎。特所感有正有邪,其动有过有不及,斯有善恶之分耳。今若以不待外感由中自发者为四端,则是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无兄而敬发矣。岂人之真情乎。今以恻隐言之,见孺子入井,然后此心乃发,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者乎?就令有之,不过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19]
栗谷强调,四端七情,人的一切心,都是感于外物而动的,没有能够无感而动的;感有正邪,动有过有不及,于是有了善恶之分。栗谷这个说法亦有未尽之处,这就是,心感外物而动,外物的感是必要的条件,但心的发动完全是以外物为条件吗?有没有内在的根据呢?朱子、退溪关于道心人心、四端七情的讨论,都重视心之所发的内在根源为何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把心之所发归结为外感。
夫人之性,有仁义礼智五者而已,五者之外,无他性。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而已,七者之外,无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别名,言七情则四端在其中矣,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对立名也。吾兄必欲立而比之,何耶。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七情之包四端,吾兄犹未见得乎。夫人之情,当喜而喜,临丧而哀,见所亲而慈爱,见理而欲穷之,见贤而欲齐之者,(已上喜哀爱欲四情)仁之端也。当怒而怒,当恶而恶者,(怒恶二情)义之端也。见尊贵而畏惧者,(惧情)礼之端也。当喜怒哀惧之际,知其所当喜所当怒所当哀所当惧,(此属是)又知其所不当喜所不当怒所不当哀所不当惧者,(此属非,此合七情而知其是非之情也)智之端也。善情之发,不可枚
举,大概如此。若以四端准于七情,则恻隐属爱,羞恶属恶,恭敬属惧,
是非属于知其当喜怒与否之情也,七情之外,更无四端矣。[20]
栗谷坚持,七情包括四端,四端作为善的情,是七情中的一部分,这是与道心人心的关系不同的。故道心人心可以做两边说,四端七情不可做两边说。如前所说,这是与高峰对退溪的异议是一致的,只是这里没有涉及气发理发的问题。
然则四端专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与人心道心之自分两
边者,岂不迥然不同乎。吾兄性有主理主气之说,虽似无害,恐是病根藏
于此中也。本然之性,则专言理而不及乎气矣。气质之性,则兼言气而包
理在其中。亦不可以主理主气之说,泛然分两边也。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
分两边,则不知者,岂不以为二性乎,且四端谓之主理,可也,七情谓之
主气则不可也。七情包理气而言,非主气也。人心道心,可作主理主气之
说,四端七情,则不可如此说,以四端在七情中,而七情兼理气故也。[21]
栗谷认为,道心人心与四端七情的关系不同,但四端七情可以与道心人心对应来看,四端对应于道心,七情则包括道心人心。他认为四端与七情的关系更类似于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因为四端专主理,七情包理气,本然之性专指理,而气质之性包括理和气,所以气质之性是包括本然之性在其中的。他对气质之性的理解合乎朱子之说。因此他反对四端主理、七情主气的说法,认为四端是七情的部分,整体包含部分,二者不能截然分两边说。四端主于理,则七情必然不能仅仅主气,必须包含主理的部分,故说七情兼理气。
其实,在此书之前,壬申年栗谷另一《答成浩原书》中已经提出:“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而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22]该书中栗谷还说:“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23]他承认七情皆发于理,道心人心皆发于性,惟发之过程中是否被气所掩,而分别成为善恶。退溪所说的理发,也是指发于理,发于性,可见栗谷后来否定理发说,只讲气发说,对他自己也是不合理的。
在退溪、高峰的辩论中,四端七情的兼理气问题,本来是与理发气发问题不同的讨论。但在二人的论辩中,在一定程度上被混同了。退溪、高峰理发气发主要是讨论四七的内在根源,兼理气的问题则是讨论现实的情感意念。高峰认为,一切现实的情感既不仅仅是理,也不仅仅是气,而是兼乎理气的。他说:“愚谓四端七情无非出于心者,而心乃理气之合,则情固兼理气也。”[24退溪也是如此,他说“理气合而为心”,又说:“二者皆不外乎理气,四端非无气,七
情非无理。”[25]其实在朱子哲学中,已发之情,不必再用理气来加分析,也就不会有气发理乘的讲法。退溪关于主于理、主于气的说法也都是指已发而言。由于他们不仅以理气来说明四端七情之所发的根源,也用理气来直接说明作为已发的四端七情本身,这是导致栗谷把四七理发气发的讨论重点从未发滑转向已发的重要原因。不过,由于朱子思想中从未对情本身做过理气分析,也未说过情即是气,所以韩国性理学对四端七情以及对整个情加以理气的分析,乃至出现各种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朱子学自身讨论的一种深入。
三
下面我们以《栗谷全书》卷十《栗谷答成浩原第二书》(即承委问)为主,对栗谷思想进一步加以分析。
理,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二者不能相离,既不能相离,则其发用一也。不可谓互有发用也。若曰互有发用,则是理发用时,气或有所不及,气发用时,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则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其错不小矣。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26]
栗谷反对理气互发说,认为讲理气互发必然导致理气有先后,理气有离合,动静有端,阴阳有始,而陷于错误。在他看来,情皆出于本然之性,这里的“出于”实等同于退溪所说的“发于”,发于本性而不受形气遮掩的四端之情,属之于理;发于本性而被形气遮掩的情,属之于气。这应该是指朱子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朱子不得已的讲法。还可以看到,就他所说的属之气的情,“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其说法实同于退溪所说的理发而气掩之。用退溪学的语言来分疏,他实际认为四端七情都是理发,即发自于理,这与高峰一致。从退溪、高峰论辩的意义上看,栗谷实际上认可四端是理发而直遂,四端以外的其他情感则是理发而气掩:
理之本然者,固是纯善,而乘气发用,善恶斯分。徒见其乘气发用有善有恶,而不知理之本然,则是不识大本也。徒见其理之本然,而不知其乘气发用,或流而为恶,则认贼为子矣。是故,圣人有忧焉,乃以情之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道心,使人存养而充广之;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本然者,目之以人心,使人审其过不及而节制之,节制之者,道心之所为也。夫形色,天性也,人心,亦岂不善乎。由其有过有不及而流于恶耳。若能充广道心,节制人心,使形色各循其则,则动静云为,莫非性命之本然矣。[27]
这一段又说到道心人心。栗谷认为,理之本然即是性,性发为情的过程就是理乘气发用的过程,情在发作过程中能直接遂成其性命之理,这样的情就被看作是道心。情在发作过程中被形气所掩蔽而不能直遂其性命之理,这样的情就被看作是人心。从退高之辩的角度看,这里所说仍然是理发直遂为道心,理发气掩则为人心。
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为乎。圣贤之千言万言,只使人捡束其气,使复其气之本然而已。气之本然者,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则本善之理,无少掩蔽。此孟子养气之论,所以有功于圣门也,若非气发理乘一途,而理亦别有作用,则不可谓理无为也。孔子何以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乎?如是看破,则气发理乘一途,明白坦然。而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亦得交通而各极其趣。试细玩详思,勿以其人之浅浅而辄轻其言也。[28]
栗谷在这里明确把其主张概括为“气发理乘”,观其所说,气发理乘具有二义:第一个意义是普遍的理气观意义,即天地之化,“气发”指天地间阴阳动静的运动,是流行之已然;“理乘”指理搭载在气上随气而动静。可见,在一般理气观的意义上,气发理乘是就存在的总体而言,即就流行之统体而言,故气发理乘不是仅仅指气,也不是仅仅指理,而是理气合一的实存流行状态。气发理乘在理气观上是指现实的、整合的存在,不是分析的概念,由此可见理气合一思想实为其根本思想。他也指出,理具有动静的所以然意义。应该说,这些提法在朱子思想中都有根据。第二个意义特指人心,即吾心之发,所以在心性论的意义上,栗谷的“气发”不是指根于气而发出,而是指心气的发动本身。他指出,讲气发理乘,并不意味着气先于理,是因为气是能动的实体,理则是无为无形的,故不得不先说气再说理。可见他在内心有着一种以能动实体为第一性的观念。
他进一步把这个思想称作“气发理乘一途”之说:
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与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通贯。吾兄尚于此处未透,故犹于退溪理气互发,内出外感,先有两个意思之说,未能尽舍,而反欲援退溪此说,附于珥说也。别幅议论颇详,犹恐兄未能涣然释然也。[29]
他认为,用气发理乘一途说,可以贯通于朱子的道心人心或原于性命或生于形气的说法,也可以贯通于朱子关于太极动静的人马比喻。他甚至认为,气发理乘是根本之论,朱子的说法则是沿流之论: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沿流之论也。今兄曰:其未发也,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此则合于鄙见矣。但谓性情之间,元有理气两物,各自出来,则此非但言语之失,实是所见差误也。又曰就一途取其重而言,此则又合于鄙见。一书之内,乍合乍离,此虽所见之不的,亦将信将疑,而将有觉悟之机也。今若知气发理乘与人信马足,马从人意,滚为一说,则同归于一,又何疑哉。道心原于性命,而发者气也,则谓之理发不可也。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焉。[30]
道心原于性命,朱子的这一观点栗谷并不反对,而他的正面观点是“发者气也,则谓之理发不可也”,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栗谷所用的理发气发,其发字不是指发自,而是指发动,因此退溪所说的气发是指根于气而发,或发自于气,是指情意思欲发动的根源;而栗谷所用的发是指发动,是运动作用的层面,不是根源的层面。因此在栗谷看来,气是现实化的力量,发动的只能是气,不能是理,因为理无为无形,理是不能活动的,于是只能说气发,不能说理发,理是不能发动、运动的。如果用已发未发的分别来看,退溪说的理发气发主要是指已发的根源,而栗谷所说的气发则是指已发的形态而言。退溪关注的是内在根源,而栗谷关注的是发动作用,二者的层次不同。前者的重点在“根源性”,后者的重点在“现实化”,退溪、栗谷都用“气发”,但二者的用法根本不同。栗谷说的发者气也,就是指已发的、发动的层面而言,因此他根本否定理发的说法。他在这里所说的人心道心都是气发,而这种说法是朱子思想中所没有的。另外,栗谷理气论、心性情论中对气的某种偏重,应与明代儒学理气论、心性论中气的因素越来越受重视有关。①
气顺乎本然之理者,固是气发,而气听命于理,故所重在理而以主理言。气变乎本然之理者,固是原于理而已,非气之本然,则不可谓听命于理也,故所重在气而以主气言。气之听命与否,皆气之所为也,理则无为也,不可谓互有发用也。但圣人形气,无非听命于理,而人心亦道心,则当别作议论,不可滚为一说也。且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发而性不发之理,则岂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非当初有理气二苗脉也。立言晓人,不得已如此。而学者之误见与否,亦非朱子所预料也。如是观之,则气发理乘与或原或生之说,果相违忤乎?[31]
所以,栗谷讲的气发是“原于理”的,用退溪的话来说这个气发是发于理的。一切意识情感都为气发,但都是发自于本然之理。由于在栗谷思想中,认为从发自本性到发作为现实意识情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气参与其中,气是现实性的力量,没有气的参与,根于本性的“发”就不能真正发作为现实的意识情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分化为两种发作的方向,一种是气顺乎本然之理,一种是气变乎本然之理,前者就发作为道心,后者则发作为人心。前者气听命于理,后者气不听命于理。栗谷把气听命于理视作主于理,把气不听命于理视作主于气;他认为朱子讲的或生于性命或生于形气,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而不应从两种根源来理解(因为在栗谷看来只有一种根源即性理)。栗谷认为,无论前者后者,都与所谓理气互发没有关系。由于四端是七情的一部分的观点和四端七情皆发自性理的观点是高峰在退高之辩中所持的观点,故栗谷的中心观点无非有二:一是认可道心人心皆出自性理,二是强调已发的道心人心(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后者是栗谷思想的重点,表现出栗谷重视已发、流行的世界的倾向。至于栗谷在这里主张气之听命与否,皆气之所为也,理则无为也,已违离了朱子道心宰制人心、人心听命道心的思想,一切归为气之所为,一切功夫只落到检束其气上,这些与朱子重视检束此心的思想也是不同的。①至于栗谷这里所说的“心是气”,把心只理解为已发之气,就更与朱子思想不同了,而有近于朱子所批评的“心为已发”说。而且,这与他自己说的七情兼理气也不一致,在栗谷,心之发当为气发而理乘,七情也是气发而理乘,他既说“七情谓之主气则不可”,又怎么能说心是气呢?
栗谷的这一说法也接近于王阳明对性气的说法。阳明曾说:“孟子性善是从本源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看始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32我曾指出,孟子所说的四端,朱子哲学称为情,而在阳明看来是气,照阳明的看法,似乎只要是“发”,就属于“气”。如果作用层次上的意识情感活动都可称为气,那么,就会导致“心即气”的说法,而这与“心即理”显然有冲突。[33]事实上,正是在明代阳明学中有很多“心即气”的说法。
其实,栗谷的这种思想,就气顺或气掩而言,用退溪的讲法,实质是理发而气顺之或理发而气掩之。而这种理发气顺的意思,和栗谷口头上所反对的退溪的理发气随说是一致的。又由于栗谷不反对退溪的气发而理乘的说法,而且将退溪专指七情的这一说法扩大到四端,这样一来,在形式上,栗谷的真正立场和退溪的“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并不全部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他其实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个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此即所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由此可见,一般认为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退溪“理发气随”,其实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做细致的思想分析,这是本文希望强调的一点。①
朱子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固然构成了朱子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和体系框架,但朱子对这些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并不都是究极性的,这一体系所包含的问题也没有被朱子个人所穷尽。因此后世朱子学对朱子的发挥、修正、扩展、深化都是朱子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这方面,朝鲜时代的朱子学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和贡献。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及展望
〔韩〕崔英辰
一、序论
如我们所知,朱子学自14世纪末传入朝鲜以后,逐步成为主导朝鲜社会发展的治国理念。建立朝鲜的主体是士大夫(即官僚兼学者),他们主导了“易姓革命”并形成了超越王权的庞大权力集团。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把重点放在了权力的分散和抑制权力的过分集中上,力求通过政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来实现以民为本的民主社会。朝鲜社会推动政策实施的主体其实就是士大夫[1],他们徘徊在辅佐和遏制王权的立场之间,创建了抑制王权的制度体系。[2]因此士大夫渐渐成了左右朝鲜王权更替的主导力量。[3]
作为官僚兼政治家的朝鲜士大夫,他们掌握实权并能参与政策的实施,所以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此外朝鲜学派和政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学术论争往往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4]朝鲜社会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学术论争,并在数百年以来持续发展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与朝鲜社会的特殊性有着很深的关联。
众所周知,朝鲜的性理学是在三次比较集中而又持续的论争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它们分别是:16世纪的“四端七情论争”、18世纪的“湖洛论争”以及19世纪的“心说论争”。四端七情论争是以“情”为中心,湖洛论争是以“性”和“未发心”为中心,心说论争则是以“心”为主题来展开。通过这三次论争,朝鲜性理学者对心性情的研究更加细致透彻,同时也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问题点。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理念,并以此确立且形成了有别于中国朱子学的韩国性理学。如此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在日本和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在三大论争中,研究成果最多的应该是“四端七情论争”。最近,对“湖洛论争”的研究也陆续展开,而对“心说论争”的研究却还处于空白状态。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心说论争”更是陌生。而它与“四端七情”和“湖洛论争”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进一步探究朝鲜性理学史的深入发展,“心说论争”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难题。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
寒洲李震相(1818~1886)在43岁时撰写的《心即理说》成了引发岭南学派内部论辩的导火索,接着也引发了与畿湖学派的激烈论辩。在《心即理说》中,寒洲批判“心是气”,强烈主张“心即理”。
朝鲜性理学从16世纪退栗时代开始,就试图用理气论来解释心和其他世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例如湖洛论争讨论“未发论”的核心问题时,提出构成未发之心的气是“湛然纯善”还是“清浊美恶”,纯善的本然之心是否是“理气同实”[5],这都是不同于朱子“中和说”的部分。而从理气论的角度去回答“心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会有“心合理气”“心即理”和“心即气”三种不同的答案。如我们所知,朱子学中把心规定为“理+气”,退溪也是主张“心合理气”。但是自栗谷主张“心是气”[6]之后,这便成了畿湖学派的宗旨。而寒洲认为“心是气”这一主张歪曲了由“孔子-孟子-朱子-退溪”所传承下来的儒学的一贯宗旨。这一点通过寒洲“论心莫善于心即理,莫不善于心即气”可以得到很好的证实。
为了批判“心是气”,寒洲提出了“心即理”,并认为自己的“心即理”才是真正传承并发展了退溪的理论。[7]但“心即理”类同于被退溪划为异端的阳明学的理论,所以不仅在岭南学派内部受到了极大的批判,在畿湖学派内部也是如此。
二、1902年~1990年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畿湖学派的其中一支是华西学派,张志渊的《朝鲜儒教的渊源》[8]一书对这一学派的心说进行了整理。书中记述了柳重教(1832~1893)和金平默(1819~1891)的观点,并简单叙述了他们对李恒老(1792~1868)心说定论的论争。李恒老是二人的恩师,柳重教在《论调补华西先生心说》中首先提出了对心说的异议,后金平默针对柳重教的论旨作《华西先生心说本义》,对恩师心说的意义进行了重申。张志渊以“京嘉两派的分裂”为题,将其分裂的过程进行了简单论述。这里的“京”是指以首尔为势力范围的洛论派系学者[9],“嘉”是指李恒老居住在“嘉陵”,即现在嘉平一带的门生。[10]由于洛论学者的学脉师承梅山洪直弼,所以这场论辩也叫作“华梅是非”。
这之后玄相允(1893~?)也对此论辩做了记载。他在《朝鲜儒学史》[11]“柳重教”一条中,对与金平默明德主理主气的论争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述。之后,裴宗镐在《韩国儒学史》[12]一书中以“明德主理主气论辩”为题,对李恒老的门人、洪直弼和吴熙常的门人,以及其再传门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做了详细叙述,他评价说“这场论争比湖洛论争更加激烈”。这三本概论书中虽然都使用了“心说”这一单词,但是却没有提及“心说论争”这一词语。
“心说论争”这一词语最开始是1983年吴锡源在《关于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研究》[13]中使用的。[14]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心说”这一词语已经包含在了华西学派内,所以使用了“心说论争”这一词语。吴锡源在论文中首先考察了李恒老的心说,然后详细考察了柳重教、金平默、崔益铉(1833~1906)对于明德的看法,最后指出了“心说论争”的特征和意义。吴锡源的论文发表之后,间或有关于朝鲜后期“心说论争”的论文出现,逐渐扩大了心说的研究范围。
吴锡源论文发表后虽然出现了有关李恒老及其学派的研究[15],但学界对于“心说论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心[16]。这是因为学界的研究方向大多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再者就以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为重点,关于心说论争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仅有两篇。
一篇是宋锡准的《对艮斋性师心第说和俛宇心即理说的考察》,1998年刊登于《艮斋学论丛》第二辑上,对艮斋的性师心第说和俛宇的心即理说进行了比较性考察。李炯性则着重考察了郭钟锡的老师李震相,对他的心即理说和以心使心论中心的主宰性进行了考察。17]以心使心虽然是首次在性理学心性论领域里被提及,但其实它是李震相心主宰性的一环。[18]
另一篇是朴洪植的《明德理气论辨》(《东洋哲学研究》第20辑,东洋哲学研究会,1999),文中指出明德理气论这一问题来源于明德主理主气的讨论,详细记述了参与此次讨论的人物及其观点,明德说以“主理”“主气”为分歧展开,“主气说”以洪直弼、任宪晦、柳重教为主,“主气说”以奇正镇、李恒老、崔益铉、李震相为主,并列举了他们的原文。
三、2000年~2009年研究领域的扩大和主要论文
近现代的性理学者虽然对性理学研究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2000年以来对性理学思想的关心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其中关于心说论辩的博士论文如下:
朴鹤来:《芦沙奇正镇的哲学思想研究》,高丽大学,2001年2月。
李炯性:《寒洲李震相的性理学研究》,成均馆大学,2001年2月。
姜弼善:《华西李恒老的哲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2002年8月。
朴性淳:《华西李恒老心主理说与斥邪论的研究——关于朝鲜后期畿湖老论洛学派心说的传承》,高丽大学,2003年8月。
李相下:《寒洲李震相性理学说的立论根据》,高丽大学,2003年12月。
李宗雨:《对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心性论争研究》,成均馆大学,2004年8月。
金勤皓:《华西李恒老的理学心论研究》,高丽大学,2008年2月。
李美林:《华西李恒老的华夷论研究》,成均馆大学,2009年2月。
以上论文中李炯性、李相下、李宗雨的论文是关于寒洲学派的,朴鹤来的论文是关于芦沙的,剩下的都是关于华西学派的。
(一)以寒洲学派为主的研究
1.关于寒洲的研究
李炯性:《寒洲李震相心即理说的含义》,《阳明学》,韩国阳明学会,2002年8月。
李宗雨:《对李震相心即理说渊源的考察》,《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03年9月。
朴祥里:《对寒洲李震相心即理说的研究》,《儒教思想研究》,韩国儒教学会,2004年8月。
李相下:《寒洲李震相心说的性质——以与岭南学派基本的心合理气说·王阳明的心即理说的差异为中心》,《东洋汉文学研究》第19辑,东洋汉文学会,2004年6月。
李炯性:《从修养论的层面来考察寒洲思想的心说》,《韩国思想和文化》第36辑,韩国思想文化学会,2007年1月。
金洛真:《以知觉说为中心来看寒洲李震相的性理学——以心即理说成立的历史背景为中心》,《东洋古典研究》第36辑,东洋古典学会,2004年9月。
权相佑,《19世纪岭南退溪学的定论与创新二重奏——从李万寅与张福枢的立场来看李震相的“心即理说”》,《南冥学研究》第28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12月。
2.对寒洲学派与艮斋学派论争的研究
李宗雨:《对寒洲与艮斋心说论争的研究——以“心即理说”和“李氏心即理说条辨”为中心》,《韩国哲学论集》第10辑,韩国哲学史研究会,2001年12月。
李宗雨:《对朱熹晚年定说论争的研究——以李震相学派和田愚学派的论争为中心》,《退溪学报》第114辑,退溪学研究院,2003年12月。
李宗雨:《李震相学派和田愚学派的知觉说论争》,《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04年3月。
李宗雨:《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对主宰论的论争及其评价》,《东洋哲学》第22辑,韩国东洋哲学会,2004年12月。
李宗雨:《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对义理实践的论争》,《韩国哲学论集》第15辑,韩国哲学史研究会,2004年9月。
李宗雨:《寒洲学派和艮斋学派对心统性情的论争及其意义》,《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05年5月。
林宗镇:《晚求李钟杞性理学的立场的考察——以与寒洲学派的论辩为中心》,《退溪学与儒教文化》第43辑,退溪研究所,2008年8月。
3.对寒洲弟子郭钟锡的研究
洪元植:《俛宇郭钟锡的明德说——以李承熙·许愈·金镇祜的论争为中心》,《南冥学研究》第27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6月。
洪元植:《俛宇郭钟锡的性理说——以对寒洲性理说的继承为中心》,《南冥学研究》第27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6月。
李相下:《俛宇郭钟锡的性理说——对寒洲性理学的继承与传播》,《南冥学研究》第28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09年12月。
4.其他
崔英辰:《对18~19世纪朝鲜性理学的心学化倾向的考察》,《韩国民族文化》第33辑,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2009年。
以上这些论文可以分为关于寒洲心说的论文,关于寒洲学派与艮斋学派论辩的论文,关于寒洲的弟子郭钟锡的论文,而崔英辰的论文则将寒洲的心即理说与湖洛论争的代表性学者李谏的“心性一致”说相联系,从朱子心学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分析、再解释。
除此之外,定斋柳致明(1777~1861)学派对寒洲学派[19]批判性考察的论文[20]、韩国阳明学者霞谷郑齐斗(1649~1736)与李震相的心性论的比较研究论文[21]也在学界发表,扩大了对李震相思想的理解范围。
(二)以寒洲学派为主的研究
李相益:《寒洲李震相的主理论及其批判》,《温知论丛》第27辑,温知学会,2011年1月。
尹丝淳:《寒洲李震相性理学式的心即理说》,《孔子学》第20辑,韩国孔子学会,2011年5月。
洪元植:《19世纪“洛上”退溪学派与“洛中”寒洲学派的分立以及性理学论争——以韩溪李承熙的“条辨”为中心》,《儒家思想文化史》第39辑,韩国儒教学会,2010年3月。
崔英辰:《19~20世纪朝鲜性理学“心即理”与“心是气”的冲突:以艮斋和重斋对寒洲“心即理”的论辩为中心》,《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2013年2月。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尹丝淳在论文中的主张:
细细体会李震相以主宰为基础的心即理说就会发现,他理论体系中的“心的主宰”就是“理的妙用”。心是意识作用,其作用就是理性的思考和
担心的情绪。也可以把他的意识作用说成是形式上“主张和宰制”,但是主宰心的体是理,也即天,这种替天主宰的方式是不是可以作用于其他地方,是不是必须只能起到这一种作用,都是需要作进一步考察的。另外从根本上说“理的主宰”本身与气的作用性质就是“名目名分”的差异,按照李震相的理论其主宰作用免不了被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规定”。
尹丝淳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李震相的心即理说,扩大了其范围。崔英辰的论文在2012年第四次国际汉学会议中儒学分科进行了初稿的发表,后经补完收录在了2013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发行的《东亚视域中的儒学:传统的解释》中。有趣的是,此书中收录了14篇论文,其中关于韩国儒学的论文就有8篇之多。论文中崔英辰考察了艮斋对寒洲心即理说的批判以及寒洲的再传弟子金榥对此的回应,并分析了他对寒洲的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三)以华西学派为主的研究
朴性淳:《毅庵柳麟锡对华西心说的传承样相》,《东方学》第27辑,东洋古典研究所,2013年5月。
金勤皓:《试论华西李恒老性理说的心学特征》,《栗谷思想研究》第26辑,栗谷学会,2013年6月。
金勤皓:《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展开过程与哲学的问题意识》,《栗谷思想研究》第27辑,栗谷学会,2013年12月。
杨祖汉:《韩国朝鲜后期儒学的心论:以华西学派为中心》,《东亚视域中的儒学:传统的解释》,2013年10月。
其中杨祖汉的论文是关于华西与其弟子省斋柳重教之间展开的心的论辩,省斋批判华西的“以理言”“以气言”,并主张将心和性严格按照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区分,将心归属于气,杨祖汉认为这是对华西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四)以艮斋学派为主的研究
艮斋学会在学术会议上考察了艮斋学派与其他学派理论的同异之处,将这些论文集结成特辑发行在《艮斋学论丛》第10辑:
林月惠:《艮斋学派与俛宇学派在思想上的同异及特征——以艮斋与俛宇的心说论争为中心》。
蔡家和:《艮斋学派与寒洲学派的思想同异及特征——田艮斋“心是气”与李寒洲“心即理”的差异比较》。
李宗雨:《艮斋学派与华西学派的思想同异及特征》。
除此之外,艮斋学派的相关研究还有:
林玉均:《艮斋田愚与醒庵李喆荣性理思想的同异和特征》,《艮斋学论丛》第14辑,艮斋学会,2012年8月。
张淑必:《艮斋与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焦点与意义》,《栗谷思想研究》第27辑,栗谷学会,2013年12月。
(五)对奇正镇(1798~1879)学派心说的研究
朴鹤来:《奇正镇的心论与明德说》,《韩国思想史学》第16辑,韩国思想史学会,2001年6月。
朴鹤来:《畿湖学界围绕奇正镇“纳凉私议”的论争》,《民族文化研究》第36辑,民族文化研究院,2010年6月。
金勤皓:《从溪南崔琡民的“明德之学”看心论》,《南冥学研究》第30辑,庆南文化研究院,2012年12月。
朴鹤来:《对芦沙奇正镇学派心说的考察》,《儒学思想文化研究》第43辑,韩国儒教学会,2011年3月。
芦沙学派认为心是理气之合,并强调精爽之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心本善”确认了心与性都是善的,从修养和实践的层面上认为心的根本体系可以实现善。朴鹤来为了阐明心说论争在道德(教育)论上的意义,对韩末性理学界的心说论争进行了考察[22],试图分析“心说论争‘以如何实现已知的人类道德本性为出发点,对心从实践层面的探讨'”。
朝鲜后期开始探讨华西学派内部的“心说论争”,其主要主旨虽然是明德主理主气,但同时也是通过认识真正的人类主体来确立人类学。
(六)其他
金景浩:《栗谷学派的心是气与其哲学的问题意识》,《栗谷思想研究》第27辑,栗谷学会,2013年。
金勤皓:《从19世纪心论的主题来看栗谷学的样相——以任宪晦、宋秉璇、李恒老、奇正镇等为中心》,《栗谷思想研究》第28辑,栗谷学会,2014年。
金景浩:《栗谷学派的心学与实学》,《韩国实学思想研究》第28辑,韩国实学学会,2014年。
以上论文都是对栗谷学心说论争焦点的阐释。
四、“心说论争”研究的新探索
韩国朱子学的三大论争是始于对心性情理气论的规定,众所周知,朱子认为四端与七情都是情感,并没有系统地对心进行理气论的规定。因此,韩国朱子学者们试图用理气论的概念来定义人类的心性,在这个理论整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很多的理论创新。
未来的研究课题如下:
韩国朱子三大论争之间的关系研究
目前为止对于各个论争的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三大论争之间的关系性研究,以及理论发展的研究则有很多不足。[23]
韩中日儒学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
抽出中日关于心说论争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可以确认韩国儒学的正统性,同时可以阐明东亚儒学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与其他学派心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与阳明学派及实学派的比较研究确立心说论争理论的特殊性。
从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立场上进行研究
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心论比较来阐明心说论争理论的特殊性。
有必要引入西方的心理学(特别是道德心理学)、脑科学等对人类心脏研究的最新现代科研成果对心说论争理论进行检证。[24](作者单位:韩国成均馆大学)
附注
①朱子门人黄榦(勉斋)亦曾论及此类问题,如黄榦与李方子书云:“发于此身者,则如喜怒哀乐是也;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混然无别矣,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勉斋黄公肃先生文集·复李公晦》)黄榦即以喜怒哀乐(七情)为发于形气之私,而以四端为发于性理之正。
①朱子学中“发于”有时也说为“出于”,如“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而在这一点上,栗谷的说法开始不清楚起来,栗谷的不清楚之处在于,他既说人心本乎天性,又说人心由乎形气,这样一来,人心究竟发自理的本性,还是发自形气之私,就被“由乎”一词变得不清楚了。本来,如果与朱子一样,栗谷只需要说道心发自本性,人心发自形气,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栗谷既要说明人心根源于本性,又要说明人心来自形气,于是便不清楚了。②早在1994年论宋时烈的一篇论文中。我曾提出对栗谷思想的分析:“他的中心论点是:发者为气,所以发者为理。因此对他来说,发是指现象的活动和活动的现象,故只能说‘气发’。而对他来说,‘理发’的说法是不通的,因为理不是现象,不是活动。由于栗谷所用的‘发’是指‘表现’,而非‘发自’,所以一方面他说的发是心之发,指意识现象,而非溯其本质(根源);另一方面,在追溯意识的本质时栗谷严格地使用‘原’‘本’,而避免使用‘发’。”(陈来:《东亚儒学九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94~115页)
①栗谷可能受到罗钦顺等的一定影响,关于罗钦顺与朝鲜性理学,朝鲜朝学者愚潭曾说:“愚意退溪则祖述朱子,洞见大体而主理,……栗谷则祖述整庵,昧于大本而所尚者气。”(《愚潭集》四七辩证)转引自张敏《立言垂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①朱子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检束此心,使无纷扰之病,即此理存也。”(《朱子语类》卷十八)
①近十年多来中文世界关于栗谷的相关研究颇不少,除诸多论文以外,专书如李甦平《韩国儒学史》、张敏《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洪军《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李明辉《四端与七情》、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等。但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在我自己虽是二十年前已经提出,诸贤似皆未加注意,故敢再提出来加以讨论。
注释:
[1]朱熹:《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四部丛刊本。
[2]朱熹:《孟子集注》卷三,四部丛刊本。
[3]朱熹:《中庸章句》第一章,四部丛刊本。
[4]李退溪:《答奇明谚论四端七情第二书》,《陶山全书》第Ⅱ部第2卷,退溪学
研究院,1988年,第42页。
[5]同上书,第46页。
[6]同上书,第49页。
[7]同上。
[8]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487页。
[9]李退溪:《圣学十图·心统性情图说》,《增补退溪全书》第一册,成均馆大学
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2年,第206页。
[10]朱熹:《朱子文集》卷二十五《答郑子中讲目》,四部丛刊本。
[11]朱熹:《朱子文集》卷十一《答李仲久》,四部丛刊本。
[12]李栗谷:《栗谷全书》卷十《答成浩原壬申》,韩国文集丛刊本。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李栗谷:《栗谷全书》卷九《答成浩原》,韩国文集丛刊本。
[23]同上。
[24]奇高峰:《附奇存斋论四端七情第二书》,《陶山全书》第Ⅱ部第2卷,退溪
学研究院,1988年,第32页。
[25]李退溪:《答奇明谚论四端七情第二书》,《陶山全书》第Ⅱ部第2卷,退溪
学研究院,1988年。
[26]李栗谷:《栗谷全书》卷十《答成浩原》,韩国文集丛刊本。
[27]同上。
[28]同上。
[29]同上。
[30]同上。
[31]同上。
[32]王阳明:《阳明全书》二《启周道通书》,四部丛刊本。
[33]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注释:
[1]韩永愚:《再觅我们历史》第二卷,经世院,2004年,第75~78页。
[2]其代表性的行政部门就是朝鲜时代的司宪部、弘文馆、司谏院,也称“言论三司”。(韩永愚:《再觅我们历史》,第78页)
[3]这与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宋明清时的国家体制有区别。李春植认为宋朝树立了君主独裁体制,明朝进一步确立了君主独裁体制,清朝完成了君主独裁体制(李春植:《中国史序说》,教保文库,2005年,第6~8章)。
[4]其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围绕王室的服丧问题而展开的礼讼论争。在第一次礼讼论争中西人胜利而掌权,而在第二次礼讼论争中南人获胜并掌权。(李泰镇等:《韩国史特讲》,首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8~169页)
[5]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34~271页。
[6]栗谷:《栗谷全书》卷10,《答成浩原》“心是气也”。
[7]《寒洲先生文集》:“(退溪)先生常曰,心之未发,气未用事,惟理而已,安有恶乎?此乃指心体之论。吾所谓莫善于心即理者,此也。”
[8]张志渊:《朝鲜儒教的渊源》,汇东书馆,1922年。
[9]代表学者有俞莘焕、赵秉直,任宪晦等,他们都师承梅山洪直弼、老洲吴熙常。
[10]代表学者有金平默、柳重教、柳重岳、柳麟锡、李声集、崔鸿锡等。
[11]玄相允:《朝鲜儒学史》,民众书林,1949年。
[12]裴宗镐:《韩国儒学史》,延世大学出版社,1974年。
[13]吴锡源:《关于华西学派心说论争的研究》,《东方思想论考——道源柳承国花甲纪念文集》,1983年,后收录在《朝鲜朝儒学思想的探究》(余江出版社,1986年)。
[14]《韩国民族大百科字典》中,在记载学者文集里,只要是关于明德主理主气的问题或是心的理气论问题就会使用“心说论争”一词。
[15]吴锡源:《对19世纪韩国道学派义理思想的研究——以华西李恒老及华西学派为中心》,成均馆大学,1992年。
[16]金炯瓒在对毅庵柳麟锡的思想进行整理时,对心说论争部分只是简单地提及了一下。(金炯瓒:《毅庵柳麟锡的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第3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2年)
[17]李炯性:《寒洲李震相的心性论研究——以心即理说和以心使心为中心》,《韩国思想和文化》,韩国思想文化学会,1998年。
[18]李炯性:《对李震相性理说中主宰性的考察——以以心使心为中心》,《东洋哲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会,1999年。
[19]关于李震相与寒洲学派的基本论文有李炯性的《寒洲李震相与其学派研究的现况与展望》(《儒教思想研究》第39辑,韩国儒教学会,2010年)。
[20]李相下:《定斋学派从心性论的立场上对寒洲学派心即理说的批判》,《儒教思想研究》第43辑,韩国儒教学会,2011年。
[21]李相勋:《霞谷郑齐斗与寒洲李震相心性论的比较研究》,第8回江华阳明学国际学术大会,韩国阳明学会,2011年10月。
[22]朴鹤来:《韩末性理学界的心说论争及其道德(教育)论的意义》,《人文科学研究论丛》第33辑,明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12月。
[23]探讨湖洛论争(未发论)与四端七情关系的论文见崔英辰《南塘与巍岩未发论的再检讨:与退溪·高峰的四端七情论辩相比较》(邢丽菊译:《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34~270页)。
[24]李允宁在《退溪与弗洛伊德心论的比较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中用精神医学的理论对退溪心性论做了比较研究。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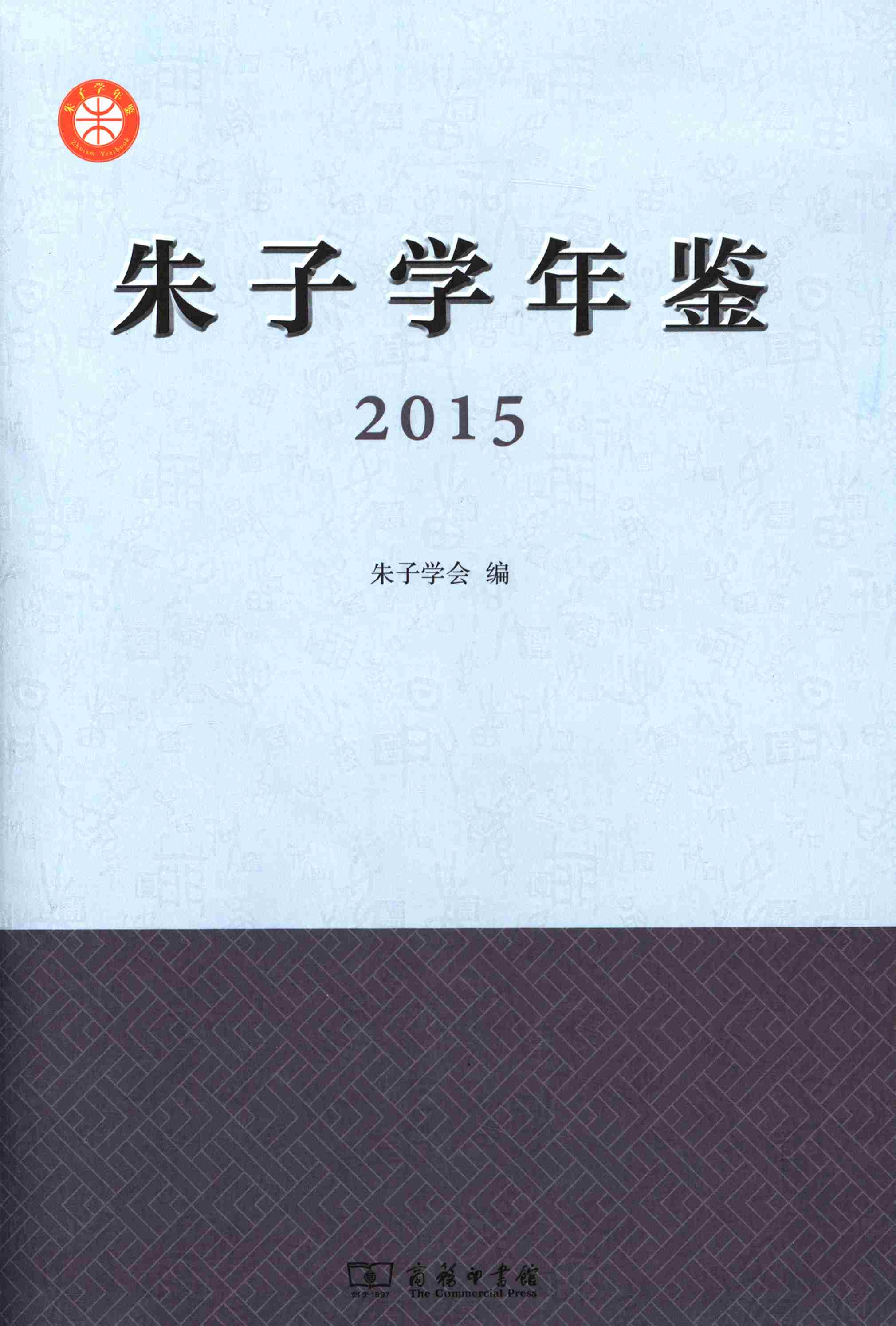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