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2018年6月26日,“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朱子学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国学院主办。共有26位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系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从多个角度对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展开讨论。
一、东亚视域下的朱子学
朱子学对中国,甚至是对整个东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以东亚的视角来看待朱子学的流传与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多元地研究与继承朱子学。
思想史的研究重要的是要对思想变动的源流脉络进行分析和厘清。日本立命馆大学桂岛宣弘教授从17世纪到18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近世帝国”概念出发,引导出18世纪末期东亚变貌与德川思想的新动向。从国民民族主义的生发、会泽安《新论》的成立、尊王攘夷思想的流传等等方面可以得出,在思想史上,儒教·朱子学的理念(“近世帝国”的理念)在东亚内部仍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因此,从东亚诸王朝的视角来看,特别是对于儒教系统的多数知识分子而言,自此以降的日本无疑就是一个单方面且暴力地破坏“近世帝国”理念的东夷。在帝国主义的暴力这一层面,尽管日本与西方诸国无异,但是上述看待日本(与西方各国不同)的视角一直持续至今,其缘由就在于上述历史背景的存在。
在研究哲学与思想史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概念的一致性。这就要求研究须以概念的确立为前提,而这一工作无疑是重要且困难的。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话语分析方法是东亚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方法论,话语分析是指对话语的语境、语义、语法、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
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具体的研究领域。东亚视域下的乡约研究可以体现出其研究的完整性、补充性的特点与优势。日本立命馆大学研究员殷晓星认为在中国和朝鲜王朝,以朱子学者、阳明学者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民众教化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的实践及学说逐渐衍生出一套相对完善的乡治理论——乡约。当今,中韩学者已就本国的乡约施行情况做了详细考证,而同一时期日本对乡约的受容研究则属空白。在对乡约流入日本社会这一事件进行考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幕末名代官早川正纪在日本推行《吕氏乡约》和闇斋学派朱子学者稻叶默斋讲解乡约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证明朱子学道德伦理在前近代东亚这一广域之内的流通,从而审视前近代东亚在民众教化史上所表现出的异同。
二、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
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是朱子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日本朱子学的源头。因此对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的研究之价值不言而喻。
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延续了他对宋明理学“人心道心”问题的研究。谢教授向大会报告了王船山人心道心思想中的“互藏交发”说,并分析了该说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谢教授指出,王船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思考存在着“互藏交发”的前说与“人心通孔”的后说,而从前说向后说的转变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原因在于,“互藏交发”说以“体用交互”说为基础,二者在理论上存在着推演关系,而“体用交互”说所具有的理论缺陷使得“互藏交发”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也陷入了理论困境。正是为了走出这一困境,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不得不转向了与朱熹相接近的“人心通孔”说。谢教授最后强调,王船山的“人心通孔”说与朱熹仍有些不同,如王船山以性情分道心人心,而朱熹则将人心道心皆视为己发。
中国儒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其内部入手,还可以从其外延切入,通过域外对儒学的认识的研究,引发对儒学自身的新思考。厦门理工学院日语系讲师陈其松认为对19世纪的西方人而言,儒教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报章中引用传教士、外交官、学者的说法,向读者介绍这个神秘国度的根本思想。面对这样一种缺乏宗教性的宗教,缺乏内在更新能力的体系,西方人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我们检视西方的新闻,可以发现中国的好坏优缺似乎总被归结为“儒教”所造成的影响。今日观之,这无疑是过度简略化的主观评判。但从文化交涉层面的角度来说,这种偏见,或者化约又是非常必须的。对异文化的贬抑或者嘲弄,其实是缓解文化冲突所产生焦虑的重要策略。化约与化减则是对异文化的概念性的归纳。在此原则之下,西方报纸中对儒教的解读讨论,呈现出“宗教性”与“文明性”,彼此存在互文关系的两个层面。儒教在宗教层面上与基督教相对照,文明性则与西方的科学与哲学相互冲撞。但不论哪一个视角,都存在对中国文化本质主义式的论述倾向,都是对“中国”及其文化文明的实质上的解读与锚定。
三、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
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研究,一方面要学习日本学界研究的框架,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搬运,而是要批判性地接受,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朱子学家林罗山对日本前近代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龚颖研究员从“四端七情”论的角度论述林罗山对朱子的承传。她认为,林罗山的心性论在“性即理”“心统性情”方面,采用了与朱熹心性论相同的表述方式,可以认为他理解并接受了朱子学心性论的这一学说。然而,朱熹认为情出于性(理)、“情=四端+七情”,而林罗山则有所不同,他尤其注重七情,几乎是把情等同于七情来把握的。林氏还把李退溪学说中的某一部分片面地加以强调、放大,认为七情全出自气,所以有很强的向恶发展的倾向,严重时能导致整个人的毁灭。林罗山的心性论思想在对情(尤其是七情)的理解和定位问题上,与朱熹和李退溪都存在重要差异。在当时江户政权由初创到确立的时期,林罗山充分认识到了战后道德秩序的重建和让饱经战乱的武士们遵守道德秩序之艰难。朱熹针对中国的士人阶层提出的“明心见性”“居敬穷理”等方法显然不能高效地应付江户初期的局面。从这种现实出发,林罗山抓住“七情”这个容易流于恶的人性弱点,强调控制情欲的重要性。
林罗山之后,荻生徂徕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研究员全面且详细地论述了徂徕学的发展与中国思想之间的关系。她从荻生徂徕的生平出发,以徂徕学以前的日本近世儒学为背景,将荻生徂徕的语言哲学作为切入点,勾勒出徂徕学的内部逻辑进路。她提出,从荻生徂徕的角度看,朱子学认为唯一的“天理”贯穿于自然、社会的所有事项当中,所以通过“居敬”“穷理”等主观的道德修养和对客观事物的考察,人有能力发现事物的本质——“天理”。在认识论上,徂徕更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反理性主义。他认为事物是无穷无尽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可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认识、掌握所有的事物的。他对“不可如之何”的“天命”的畏惧反映了在封建身份制社会里,人被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所限制,对人类自身能力局限性消极妥协,这使徂徕学比朱子学更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徂徕认为礼乐刑政因为是圣人“法天”而立,所以是权威,先王之道(当然包括五伦常等道德规范)先验地与“天命”是一致的,而且唯一的媒介物就是圣人,就这样徂徕对朱子学的“合理主义”展开了批判。
稍早于荻生徂徕的伊藤仁斋,不仅在哲学学说上有很大成就,同时在政治思想与道德伦理思想上也有重大影响。武汉大学国学院助理教授陈晓杰认为,仁斋依据孟子之主张,以“同民之好恶”作为王道论之基本原则。但是,“同民之好恶”的说法本来就存在多义性与暧昧性,仁斋对其理解也存在模糊之处。在仁斋眼中,“化民成俗”或者“风教”论之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是君主,除此以外的人试图改变民风或者修订礼乐等都是僭越之举。反观中国,通过科举考试之选拔而参与政治的儒者士大夫阶层,大都秉承着“与陛下共理天下”的信念,积极地介入地方社会,实践“化民成俗”。他们并非完全超越于社会,而是作为地方社会全体构成中一个有力的参与者,因而即便要“化民成俗”也未必能实现,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实践与努力并不能算是“僭越”——因为就身份而言他们都属于统治集团而并非一介匹夫。由此可见,仁斋所考虑的“君主—庶民”之政治构造过于平板化,完全忽视了既非天子,也非匹夫的中间阶层,亦即士大夫之存在,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朱熹、王阳明等儒家努力改善民风方面的意义所在。
儒学的教化意义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教授认为,明治时代可谓是儒学真正走向“日本化”的时代,最为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形成了“儒教的国家体制”。不过,这一体制的形成经历了幕府末期以来的儒学教育批判,经历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西学转向,也经历了明治维新改革滞后的重大挫折,而后在汉学家的推动下得以复活,与日本天皇制的国家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大羽翼。以日本固有的道德教育为核心,依据儒教主义来树立近代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说也是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一思想,不仅标志着日本式的儒教主义的复兴,也标志了明治初期的启蒙开化主义业已达到了“临界”状态,同时也预示了无论是儒教主义还是启蒙开化主义,皆必然归结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势。
除了对思想本身的研究,文献学、考证学的研究同样十分重要。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认为,江户时代的儒学,在考证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类似中国本土的朴学学风。校勘学就是江户时代日本考证学的重要领域及贡献之一,明治时代岛田翰(1879~1915,字彦桢)所提出的“明治校勘学”也是在此之上发展形成的概念。遗憾的是,日本儒学家的贡献却大多不为人所知。《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二书则是日本《论语》学成就的代表,这两部新疏不仅总结了中国历代注释及本国前人儒学家的学说,折中论断,在校勘上亦持有审慎细致的态度,运用本国所藏诸古本及古注,自出手眼,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的《论语》研究者,长期以来几乎不知《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二书的存在,包括近代以来的主要的汇注本对两者的学说及校勘成果也未能加以利用。我国对于江户日本儒学家的汉籍校勘,除了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安井息轩《管子纂诂》等极少数书籍外,了解与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充分了解江户日本儒学家的贡献,利用其成果,则是当前《论语》研究者的责任之一。
日本儒学不仅体现在儒者的哲学性论述中,还能够渗透进入文学之中,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毅立、李桐提出,“汉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深入,“汉诗”进入日本并发扬光大。江户时期,以儒学为奠基的“汉诗”创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幕府的余晖消失殆尽,封建与维新、旧道德与新思想交错之际,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吉田松阴正是其中的代表。历来研究多把松阴塑造为“革命家”“教育家”“兵学家”,对其文学(诗歌)思想的考察却门庭冷落。松阴在诗中对道义之咏叹及对时局之批判不仅充分体现了其“拳头观宇宙,大道到处随”的经世济民情怀,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川幕末的悸动与波澜。
本次会议首次使用了“日本朱子学”的概念作为会议主题,可以说是日本朱子学发展的里程碑。与会学者集中而有效的讨论,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不仅对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日本朱子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拓展。会议的圆满召开无疑为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提供了强大助力!
一、东亚视域下的朱子学
朱子学对中国,甚至是对整个东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以东亚的视角来看待朱子学的流传与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多元地研究与继承朱子学。
思想史的研究重要的是要对思想变动的源流脉络进行分析和厘清。日本立命馆大学桂岛宣弘教授从17世纪到18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近世帝国”概念出发,引导出18世纪末期东亚变貌与德川思想的新动向。从国民民族主义的生发、会泽安《新论》的成立、尊王攘夷思想的流传等等方面可以得出,在思想史上,儒教·朱子学的理念(“近世帝国”的理念)在东亚内部仍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因此,从东亚诸王朝的视角来看,特别是对于儒教系统的多数知识分子而言,自此以降的日本无疑就是一个单方面且暴力地破坏“近世帝国”理念的东夷。在帝国主义的暴力这一层面,尽管日本与西方诸国无异,但是上述看待日本(与西方各国不同)的视角一直持续至今,其缘由就在于上述历史背景的存在。
在研究哲学与思想史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概念的一致性。这就要求研究须以概念的确立为前提,而这一工作无疑是重要且困难的。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认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话语分析方法是东亚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方法论,话语分析是指对话语的语境、语义、语法、产生、发展、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方法。
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具体的研究领域。东亚视域下的乡约研究可以体现出其研究的完整性、补充性的特点与优势。日本立命馆大学研究员殷晓星认为在中国和朝鲜王朝,以朱子学者、阳明学者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民众教化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的实践及学说逐渐衍生出一套相对完善的乡治理论——乡约。当今,中韩学者已就本国的乡约施行情况做了详细考证,而同一时期日本对乡约的受容研究则属空白。在对乡约流入日本社会这一事件进行考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幕末名代官早川正纪在日本推行《吕氏乡约》和闇斋学派朱子学者稻叶默斋讲解乡约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证明朱子学道德伦理在前近代东亚这一广域之内的流通,从而审视前近代东亚在民众教化史上所表现出的异同。
二、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
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是朱子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日本朱子学的源头。因此对中国视域下的朱子学的研究之价值不言而喻。
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延续了他对宋明理学“人心道心”问题的研究。谢教授向大会报告了王船山人心道心思想中的“互藏交发”说,并分析了该说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谢教授指出,王船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思考存在着“互藏交发”的前说与“人心通孔”的后说,而从前说向后说的转变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原因在于,“互藏交发”说以“体用交互”说为基础,二者在理论上存在着推演关系,而“体用交互”说所具有的理论缺陷使得“互藏交发”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也陷入了理论困境。正是为了走出这一困境,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不得不转向了与朱熹相接近的“人心通孔”说。谢教授最后强调,王船山的“人心通孔”说与朱熹仍有些不同,如王船山以性情分道心人心,而朱熹则将人心道心皆视为己发。
中国儒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其内部入手,还可以从其外延切入,通过域外对儒学的认识的研究,引发对儒学自身的新思考。厦门理工学院日语系讲师陈其松认为对19世纪的西方人而言,儒教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报章中引用传教士、外交官、学者的说法,向读者介绍这个神秘国度的根本思想。面对这样一种缺乏宗教性的宗教,缺乏内在更新能力的体系,西方人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我们检视西方的新闻,可以发现中国的好坏优缺似乎总被归结为“儒教”所造成的影响。今日观之,这无疑是过度简略化的主观评判。但从文化交涉层面的角度来说,这种偏见,或者化约又是非常必须的。对异文化的贬抑或者嘲弄,其实是缓解文化冲突所产生焦虑的重要策略。化约与化减则是对异文化的概念性的归纳。在此原则之下,西方报纸中对儒教的解读讨论,呈现出“宗教性”与“文明性”,彼此存在互文关系的两个层面。儒教在宗教层面上与基督教相对照,文明性则与西方的科学与哲学相互冲撞。但不论哪一个视角,都存在对中国文化本质主义式的论述倾向,都是对“中国”及其文化文明的实质上的解读与锚定。
三、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
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研究,一方面要学习日本学界研究的框架,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搬运,而是要批判性地接受,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朱子学家林罗山对日本前近代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龚颖研究员从“四端七情”论的角度论述林罗山对朱子的承传。她认为,林罗山的心性论在“性即理”“心统性情”方面,采用了与朱熹心性论相同的表述方式,可以认为他理解并接受了朱子学心性论的这一学说。然而,朱熹认为情出于性(理)、“情=四端+七情”,而林罗山则有所不同,他尤其注重七情,几乎是把情等同于七情来把握的。林氏还把李退溪学说中的某一部分片面地加以强调、放大,认为七情全出自气,所以有很强的向恶发展的倾向,严重时能导致整个人的毁灭。林罗山的心性论思想在对情(尤其是七情)的理解和定位问题上,与朱熹和李退溪都存在重要差异。在当时江户政权由初创到确立的时期,林罗山充分认识到了战后道德秩序的重建和让饱经战乱的武士们遵守道德秩序之艰难。朱熹针对中国的士人阶层提出的“明心见性”“居敬穷理”等方法显然不能高效地应付江户初期的局面。从这种现实出发,林罗山抓住“七情”这个容易流于恶的人性弱点,强调控制情欲的重要性。
林罗山之后,荻生徂徕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研究员全面且详细地论述了徂徕学的发展与中国思想之间的关系。她从荻生徂徕的生平出发,以徂徕学以前的日本近世儒学为背景,将荻生徂徕的语言哲学作为切入点,勾勒出徂徕学的内部逻辑进路。她提出,从荻生徂徕的角度看,朱子学认为唯一的“天理”贯穿于自然、社会的所有事项当中,所以通过“居敬”“穷理”等主观的道德修养和对客观事物的考察,人有能力发现事物的本质——“天理”。在认识论上,徂徕更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反理性主义。他认为事物是无穷无尽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可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认识、掌握所有的事物的。他对“不可如之何”的“天命”的畏惧反映了在封建身份制社会里,人被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所限制,对人类自身能力局限性消极妥协,这使徂徕学比朱子学更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徂徕认为礼乐刑政因为是圣人“法天”而立,所以是权威,先王之道(当然包括五伦常等道德规范)先验地与“天命”是一致的,而且唯一的媒介物就是圣人,就这样徂徕对朱子学的“合理主义”展开了批判。
稍早于荻生徂徕的伊藤仁斋,不仅在哲学学说上有很大成就,同时在政治思想与道德伦理思想上也有重大影响。武汉大学国学院助理教授陈晓杰认为,仁斋依据孟子之主张,以“同民之好恶”作为王道论之基本原则。但是,“同民之好恶”的说法本来就存在多义性与暧昧性,仁斋对其理解也存在模糊之处。在仁斋眼中,“化民成俗”或者“风教”论之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是君主,除此以外的人试图改变民风或者修订礼乐等都是僭越之举。反观中国,通过科举考试之选拔而参与政治的儒者士大夫阶层,大都秉承着“与陛下共理天下”的信念,积极地介入地方社会,实践“化民成俗”。他们并非完全超越于社会,而是作为地方社会全体构成中一个有力的参与者,因而即便要“化民成俗”也未必能实现,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实践与努力并不能算是“僭越”——因为就身份而言他们都属于统治集团而并非一介匹夫。由此可见,仁斋所考虑的“君主—庶民”之政治构造过于平板化,完全忽视了既非天子,也非匹夫的中间阶层,亦即士大夫之存在,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朱熹、王阳明等儒家努力改善民风方面的意义所在。
儒学的教化意义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教授认为,明治时代可谓是儒学真正走向“日本化”的时代,最为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形成了“儒教的国家体制”。不过,这一体制的形成经历了幕府末期以来的儒学教育批判,经历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西学转向,也经历了明治维新改革滞后的重大挫折,而后在汉学家的推动下得以复活,与日本天皇制的国家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大羽翼。以日本固有的道德教育为核心,依据儒教主义来树立近代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说也是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一思想,不仅标志着日本式的儒教主义的复兴,也标志了明治初期的启蒙开化主义业已达到了“临界”状态,同时也预示了无论是儒教主义还是启蒙开化主义,皆必然归结为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势。
除了对思想本身的研究,文献学、考证学的研究同样十分重要。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认为,江户时代的儒学,在考证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类似中国本土的朴学学风。校勘学就是江户时代日本考证学的重要领域及贡献之一,明治时代岛田翰(1879~1915,字彦桢)所提出的“明治校勘学”也是在此之上发展形成的概念。遗憾的是,日本儒学家的贡献却大多不为人所知。《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二书则是日本《论语》学成就的代表,这两部新疏不仅总结了中国历代注释及本国前人儒学家的学说,折中论断,在校勘上亦持有审慎细致的态度,运用本国所藏诸古本及古注,自出手眼,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的《论语》研究者,长期以来几乎不知《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二书的存在,包括近代以来的主要的汇注本对两者的学说及校勘成果也未能加以利用。我国对于江户日本儒学家的汉籍校勘,除了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安井息轩《管子纂诂》等极少数书籍外,了解与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充分了解江户日本儒学家的贡献,利用其成果,则是当前《论语》研究者的责任之一。
日本儒学不仅体现在儒者的哲学性论述中,还能够渗透进入文学之中,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毅立、李桐提出,“汉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深入,“汉诗”进入日本并发扬光大。江户时期,以儒学为奠基的“汉诗”创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幕府的余晖消失殆尽,封建与维新、旧道德与新思想交错之际,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吉田松阴正是其中的代表。历来研究多把松阴塑造为“革命家”“教育家”“兵学家”,对其文学(诗歌)思想的考察却门庭冷落。松阴在诗中对道义之咏叹及对时局之批判不仅充分体现了其“拳头观宇宙,大道到处随”的经世济民情怀,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川幕末的悸动与波澜。
本次会议首次使用了“日本朱子学”的概念作为会议主题,可以说是日本朱子学发展的里程碑。与会学者集中而有效的讨论,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不仅对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日本朱子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拓展。会议的圆满召开无疑为日本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提供了强大助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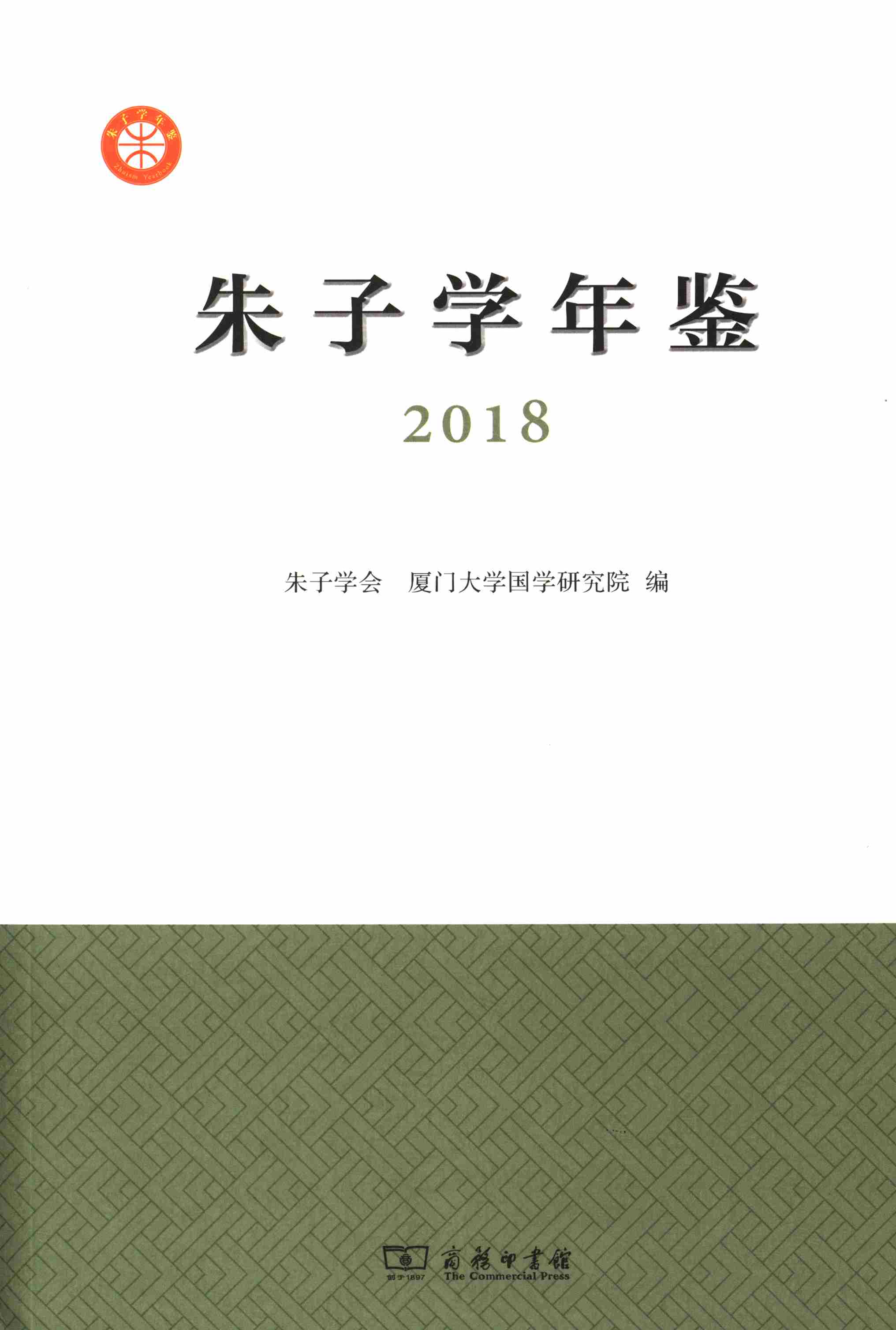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何浩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