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与“文字”之间的“吾道之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8)》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334 |
| 颗粒名称: | “言语”与“文字”之间的“吾道之寄” |
| 其他题名: | 《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读后感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154-159 |
| 摘要: | 本篇文章讨论了苏费翔、田浩两位教授合著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英文版出版的情况,以及该书在拓展朱子学研究视野方面的创新性。同时,文章还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包括对宋代《中庸》与道统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朱熹道统观念的探讨。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视野 道统问题 |
内容
苏费翔、田浩两位教授合著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笔者2018年6月方得捧读由肖永明教授译成的中文版(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下简称《文化权力》);同年7月份赴特里尔大学参加苏费翔教授主持的“朱子学国际研讨会”,8月份参加复旦大学“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又有幸分别向苏费翔、田浩两位教授当面请教,获益良多,深感本书在拓展朱子学研究视野方面具有独特的创新性,故不揣浅陋,谈点读后感,就教于方家。
长期以来,朱熹首创的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围绕着朱熹的道统观念,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议题:第一个问题,在朱熹直至明初,朱子学是怎样成为“新道统”的;第二个问题,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提出的道统谱系,到底是一个历史的阐释,还是哲学的信仰(“道之正”)?对于这两个议题,该书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章)集中讨论了宋代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该书对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的相关讨论说明,虽然在“程朱正统”的大力褒扬下,《中庸》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和“道统”的核心依据,但即使到了崇拜理学的南宋晚期,《中庸》的作者问题、解释问题(分章断句),仍然是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开放的学术问题,即使在程朱理学系统之内也存在着不同于朱熹的看法(譬如王柏),对《中庸》的怀疑和批评实际上贯穿了两宋,这些声音不应被忽视。该书第三章对“道统”观念的讨论还指出,无论朱熹之前还是之后,宋代学术界都存在着不同于朱熹的“道统”论述。可见,自朱熹去世之后(1200)到明初,朱子学持续地处在官学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之中,但由于宋元、元明两次易代造成的政治转折,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其中不乏争议、停滞乃至倒退。
该书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一、“道统”是不是“客观的学统”?
黄榦(1152~1221)在《朱文公行状》中写道:“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道统”即“道之正统”。这样一来,朱熹道统说必然建于两个基点之上:何为“道之正”,何为“道之统”?“道之正”主要回答什么是道之本体的问题,而每一种新的道统观论说的出现,都是因为对道之本体的认识发生了突变,遂根据新的认知对道统谱系进行新的厘定和判教。“道之统”,则指道在历史时空中呈现的传承脉络,这一脉络表现为由学者组成的谱系,即黄榦所谓“待人而后传”。
但是,“道之统”与“道之正”是什么关系呢?陈荣捷教授认为:“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进一步言之,即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内在需要。”[1]“道统”的确立,并不以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人际关系,或者文献记载为根据,而是根据构建道统者本人的哲学思想,选取历史上的人物组成道统谱系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延续性,道统谱系本身也是为了论证一个自洽的哲学逻辑系统而成立的。
1982年,刘述先先生发表了《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2],比较系统地发挥了陈荣捷先生关于朱子学道统的哲学性本质的论说,指出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具体论证了程朱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我们至少可以说,宋儒是在不违背孔孟的基本精神之下,受到佛老的冲击,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儒家的思想。”根据这套思想标准,宋儒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是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这样一来,“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只要认识到“道统”“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信仰的对象”,那么道统自然可以成立:
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由纯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3]
刘先生所谓“客观的学统”当指学者之间的授受关系,诚然,朱熹所提出的道统谱系中,有多个环节是断裂的、跳跃的,特别是从孟子到北宋二程之间,长达千余年的空缺。那么是否可以说道统的“道之正”并不需要任何文献的依据呢?刘述先先生对此做了一个很谨慎的分辨:
如果以宋学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饾饤考据的工作。始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文义的引申,不只不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这样的解释可能越出了古典的原义,正如海德格所谓的doingviolence to the text,但却不一定违反原典的精神。而慧识的传递,比章句的解释,对宋儒来说,显然是有更重要的价值。[4]
宋儒面对先秦的文本,一开始由文字的解释而入,接着又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所引申出来的见解可能不符合文本的“原义”,但这是“慧解的印证”,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错误或过失。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道:“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5]“心传道统”一语正反映了“慧解的印证”。
《文化权力》在处理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对陈、刘两位教授的解释框架提出了基于历史考据立场的质疑,即从历史考据的角度看,《中庸》是否是一部“真正的”儒家经典?子思是否是《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否是曾子的弟子?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朱熹以《中庸》为核心的道统论是否就不能成立?该书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对《中庸》的怀疑,其中不少内容仍然属于哲学思辨的范畴(“慧解的印证”),可谓见仁见智,这里不做评判。但作者基于历史考证的角度,梳理了两宋学者对《中庸》作者的怀疑,论证了子思是否是《中庸》作者、子思与曾子的师徒关系这两个先秦时期的“历史真相”的可靠性,得出结论是《中庸》很可能不是子思所撰[6],子思与曾子也很可能没有师徒关系[7]。由此,《文化权力》质疑了朱熹的学术严谨性。那么,朱熹是不是像陈、刘两位先生和《文化权力》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无视“道统”的客观性,从而回避了历史考据学的难点呢?
二、朱熹对“道统”客观性的尊重
首先应该看到,朱熹主张子思撰《中庸》自有其传统的历史证据。此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郑玄《三礼目录》也确认了子思是《礼记·中庸》的作者;即便是《文化权力》所引用的欧阳修《策问》[8]也只是怀疑子思“疑其传之谬也”,即《中庸》的思想内容不能代表儒学的正统,而未否认子思是《中庸》的作者。至于苏轼,该书也承认:“与欧阳修不同的是,苏轼仍然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9]在《文化权力》中,真正质疑“汉人虽称《中庸》为子思所著,今以《书》考之,疑其(《中庸》)不专出子思”的是叶适,然而此说出自《习学记言序目》,此书于朱熹去世后23年(1223)刊刻,朱熹已无法参考。曾子和子思的师徒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礼记·檀弓》两处记载子思曾向曾子求教,《孟子》也曾提到:“曾子,师也。”也许,《檀弓》不一定是“周代的文献”,但至今尚无更早的可靠证据可以反证此说。总之,由于“历史真相”的极端复杂性和相关证据的缺失,应该还没有宋代学者能够提出更早的文献证据推翻司马迁和郑玄的定论(包括叶适),自然也不能批评朱熹在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如其他宋代学者那样“严谨缜密、深思熟虑”[10]了。
在处理子思与孟子师徒关系可靠性问题时,朱熹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考据学意义上的严谨。孟子的师承问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赵岐《孟子章句》则以为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隋人王劭之说,以“人”字为衍文,当作“受业子思之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写道:“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11]朱熹指出孟子的贡献在于能够“推明此书,以承先圣之统”,通过研习《中庸》而传道的,并未亲炙子思。但到了《中庸章句》卷首“子程子曰”至“有不能尽者矣”这段跋语中,朱熹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12]如此,子思与孟子不仅是亲相授受,而且子思还授之以《中庸》。最后在《孟子集注卷首》中,朱熹征引了《史记索隐》王劭说及赵岐、《孔丛子》各说,而结论却是:“未知是否?”仍不敢定论。
《中庸章句序》与《中庸章句卷首跋语》《孟子集注卷首》三者对思孟师徒关系的表述的差异,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朱熹在构建“道统”谱系时,对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问题是谨慎而深思熟虑的,并未因为偏爱师徒授受关系而轻易排除那些明显的反证;第二,子思与孟子亲相授受(亲传面授)是否成立,根本上不会对朱熹构建其道统谱系造成损害。
三、承载“道统”的“言语”和“文字”
根据朱熹的道统论述,道统的上一环节与下一环节可以相距一千余年(譬如周敦颐与孟子),道统的传承显然并不单纯依赖师徒授受的关系,孟子即便没有见过子思,但他通过《中庸》一书发现了子思之道,从而接续了道统。故《中庸章句序》云:“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13]“言语”和“文字”各具意蕴:“言语”显然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即师徒之间亲相授受;“文字”无疑就是经典文本,《中庸》就是“吾道之所寄”的“言语文字之间”的“文字”。根据《中庸章句序》,子思撰《中庸》时,并未预见哪位后学能发现《中庸》所蕴含的“道”,但文献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公开性,故子思试图通过《中庸》“以诏后之学者”。同理,孟子也许未曾亲受业于子思,但由于《中庸》等经典文本是向所有潜在的读者敞开的,因此孟子仍可通过《中庸》的语言,得“子思之心”“孔子之心”乃至“上古圣神之心”。故《中庸章句序》说,孟子的功劳在于“推明是书(《中庸》)”,二程的功劳在于“因其语而得其心”,即通过《中庸》的文本而得到了上一个传道者孟子之“心”。
由于师徒遇合不易,道经常无法以“言语”的形式传承,但经典文本较易存留,只要《中庸》存在于历史时空之中,道就有可能被重新发现,因此“言语、文字”二者之中,“文字”是更可靠的传道中介,曾子见过子思或者只是见过子思之门人,并不能损害其所传之道的价值。在朱熹的道统观中,“道统是由老师传授给学生的谱系这一方面的色彩”,并非如《文化权力》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强化”[14],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该书所引用的李流谦《上张和公书》中所云:“至于列圣之道统……盖未可以笔舌授而闻得也。”[15恰恰主张“言语文字”是不可靠的,不足以传道,这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主张并无任何相似性,更不能由此推导出“朱熹有可能从张氏家族成员那里听到过‘道统’一词”的结论[16]。
在论及那些跨越时空的传道环节时,正如陈荣捷、刘述先两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朱熹主要根据哲学意义的“慧解的印证”来建立道统传承的谱系。但即使是“慧解的印证”,朱熹仍接续道统之传必须有文献(“文字”)的依据,传道者是通过阐释上一代传道者所撰写的经典而得到领悟。于是,上一个传道者与下一个传道者之间虽然存在千余年历史间隔,但通过文献依据或师承渊源,历代传道者都被纳入了一种历史时间的序列或“经籍”的序列之中,从而使道统在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论证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约束。
因此,《文化权力》尝试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质疑朱熹道统谱系的努力虽然未臻完善,但其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醒我们,在研究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客观的学统”并不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道统与学统”并非“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不可调和;相反,朱熹在肯定“心传道统”的前提下,形成了“因其语而得其心”的道统论述;而这一论述正是由客观性(历史性)与主观性(哲学性)两者有机统合而成的,不可偏废。
长期以来,朱熹首创的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围绕着朱熹的道统观念,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议题:第一个问题,在朱熹直至明初,朱子学是怎样成为“新道统”的;第二个问题,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提出的道统谱系,到底是一个历史的阐释,还是哲学的信仰(“道之正”)?对于这两个议题,该书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章)集中讨论了宋代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该书对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的相关讨论说明,虽然在“程朱正统”的大力褒扬下,《中庸》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和“道统”的核心依据,但即使到了崇拜理学的南宋晚期,《中庸》的作者问题、解释问题(分章断句),仍然是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开放的学术问题,即使在程朱理学系统之内也存在着不同于朱熹的看法(譬如王柏),对《中庸》的怀疑和批评实际上贯穿了两宋,这些声音不应被忽视。该书第三章对“道统”观念的讨论还指出,无论朱熹之前还是之后,宋代学术界都存在着不同于朱熹的“道统”论述。可见,自朱熹去世之后(1200)到明初,朱子学持续地处在官学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之中,但由于宋元、元明两次易代造成的政治转折,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其中不乏争议、停滞乃至倒退。
该书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一、“道统”是不是“客观的学统”?
黄榦(1152~1221)在《朱文公行状》中写道:“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道统”即“道之正统”。这样一来,朱熹道统说必然建于两个基点之上:何为“道之正”,何为“道之统”?“道之正”主要回答什么是道之本体的问题,而每一种新的道统观论说的出现,都是因为对道之本体的认识发生了突变,遂根据新的认知对道统谱系进行新的厘定和判教。“道之统”,则指道在历史时空中呈现的传承脉络,这一脉络表现为由学者组成的谱系,即黄榦所谓“待人而后传”。
但是,“道之统”与“道之正”是什么关系呢?陈荣捷教授认为:“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进一步言之,即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内在需要。”[1]“道统”的确立,并不以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人际关系,或者文献记载为根据,而是根据构建道统者本人的哲学思想,选取历史上的人物组成道统谱系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延续性,道统谱系本身也是为了论证一个自洽的哲学逻辑系统而成立的。
1982年,刘述先先生发表了《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2],比较系统地发挥了陈荣捷先生关于朱子学道统的哲学性本质的论说,指出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具体论证了程朱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我们至少可以说,宋儒是在不违背孔孟的基本精神之下,受到佛老的冲击,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儒家的思想。”根据这套思想标准,宋儒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是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这样一来,“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只要认识到“道统”“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信仰的对象”,那么道统自然可以成立:
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由纯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3]
刘先生所谓“客观的学统”当指学者之间的授受关系,诚然,朱熹所提出的道统谱系中,有多个环节是断裂的、跳跃的,特别是从孟子到北宋二程之间,长达千余年的空缺。那么是否可以说道统的“道之正”并不需要任何文献的依据呢?刘述先先生对此做了一个很谨慎的分辨:
如果以宋学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饾饤考据的工作。始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文义的引申,不只不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这样的解释可能越出了古典的原义,正如海德格所谓的doingviolence to the text,但却不一定违反原典的精神。而慧识的传递,比章句的解释,对宋儒来说,显然是有更重要的价值。[4]
宋儒面对先秦的文本,一开始由文字的解释而入,接着又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所引申出来的见解可能不符合文本的“原义”,但这是“慧解的印证”,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错误或过失。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道:“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5]“心传道统”一语正反映了“慧解的印证”。
《文化权力》在处理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对陈、刘两位教授的解释框架提出了基于历史考据立场的质疑,即从历史考据的角度看,《中庸》是否是一部“真正的”儒家经典?子思是否是《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否是曾子的弟子?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朱熹以《中庸》为核心的道统论是否就不能成立?该书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对《中庸》的怀疑,其中不少内容仍然属于哲学思辨的范畴(“慧解的印证”),可谓见仁见智,这里不做评判。但作者基于历史考证的角度,梳理了两宋学者对《中庸》作者的怀疑,论证了子思是否是《中庸》作者、子思与曾子的师徒关系这两个先秦时期的“历史真相”的可靠性,得出结论是《中庸》很可能不是子思所撰[6],子思与曾子也很可能没有师徒关系[7]。由此,《文化权力》质疑了朱熹的学术严谨性。那么,朱熹是不是像陈、刘两位先生和《文化权力》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无视“道统”的客观性,从而回避了历史考据学的难点呢?
二、朱熹对“道统”客观性的尊重
首先应该看到,朱熹主张子思撰《中庸》自有其传统的历史证据。此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郑玄《三礼目录》也确认了子思是《礼记·中庸》的作者;即便是《文化权力》所引用的欧阳修《策问》[8]也只是怀疑子思“疑其传之谬也”,即《中庸》的思想内容不能代表儒学的正统,而未否认子思是《中庸》的作者。至于苏轼,该书也承认:“与欧阳修不同的是,苏轼仍然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9]在《文化权力》中,真正质疑“汉人虽称《中庸》为子思所著,今以《书》考之,疑其(《中庸》)不专出子思”的是叶适,然而此说出自《习学记言序目》,此书于朱熹去世后23年(1223)刊刻,朱熹已无法参考。曾子和子思的师徒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礼记·檀弓》两处记载子思曾向曾子求教,《孟子》也曾提到:“曾子,师也。”也许,《檀弓》不一定是“周代的文献”,但至今尚无更早的可靠证据可以反证此说。总之,由于“历史真相”的极端复杂性和相关证据的缺失,应该还没有宋代学者能够提出更早的文献证据推翻司马迁和郑玄的定论(包括叶适),自然也不能批评朱熹在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如其他宋代学者那样“严谨缜密、深思熟虑”[10]了。
在处理子思与孟子师徒关系可靠性问题时,朱熹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考据学意义上的严谨。孟子的师承问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赵岐《孟子章句》则以为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隋人王劭之说,以“人”字为衍文,当作“受业子思之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写道:“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11]朱熹指出孟子的贡献在于能够“推明此书,以承先圣之统”,通过研习《中庸》而传道的,并未亲炙子思。但到了《中庸章句》卷首“子程子曰”至“有不能尽者矣”这段跋语中,朱熹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12]如此,子思与孟子不仅是亲相授受,而且子思还授之以《中庸》。最后在《孟子集注卷首》中,朱熹征引了《史记索隐》王劭说及赵岐、《孔丛子》各说,而结论却是:“未知是否?”仍不敢定论。
《中庸章句序》与《中庸章句卷首跋语》《孟子集注卷首》三者对思孟师徒关系的表述的差异,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朱熹在构建“道统”谱系时,对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问题是谨慎而深思熟虑的,并未因为偏爱师徒授受关系而轻易排除那些明显的反证;第二,子思与孟子亲相授受(亲传面授)是否成立,根本上不会对朱熹构建其道统谱系造成损害。
三、承载“道统”的“言语”和“文字”
根据朱熹的道统论述,道统的上一环节与下一环节可以相距一千余年(譬如周敦颐与孟子),道统的传承显然并不单纯依赖师徒授受的关系,孟子即便没有见过子思,但他通过《中庸》一书发现了子思之道,从而接续了道统。故《中庸章句序》云:“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13]“言语”和“文字”各具意蕴:“言语”显然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即师徒之间亲相授受;“文字”无疑就是经典文本,《中庸》就是“吾道之所寄”的“言语文字之间”的“文字”。根据《中庸章句序》,子思撰《中庸》时,并未预见哪位后学能发现《中庸》所蕴含的“道”,但文献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公开性,故子思试图通过《中庸》“以诏后之学者”。同理,孟子也许未曾亲受业于子思,但由于《中庸》等经典文本是向所有潜在的读者敞开的,因此孟子仍可通过《中庸》的语言,得“子思之心”“孔子之心”乃至“上古圣神之心”。故《中庸章句序》说,孟子的功劳在于“推明是书(《中庸》)”,二程的功劳在于“因其语而得其心”,即通过《中庸》的文本而得到了上一个传道者孟子之“心”。
由于师徒遇合不易,道经常无法以“言语”的形式传承,但经典文本较易存留,只要《中庸》存在于历史时空之中,道就有可能被重新发现,因此“言语、文字”二者之中,“文字”是更可靠的传道中介,曾子见过子思或者只是见过子思之门人,并不能损害其所传之道的价值。在朱熹的道统观中,“道统是由老师传授给学生的谱系这一方面的色彩”,并非如《文化权力》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强化”[14],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该书所引用的李流谦《上张和公书》中所云:“至于列圣之道统……盖未可以笔舌授而闻得也。”[15恰恰主张“言语文字”是不可靠的,不足以传道,这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主张并无任何相似性,更不能由此推导出“朱熹有可能从张氏家族成员那里听到过‘道统’一词”的结论[16]。
在论及那些跨越时空的传道环节时,正如陈荣捷、刘述先两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朱熹主要根据哲学意义的“慧解的印证”来建立道统传承的谱系。但即使是“慧解的印证”,朱熹仍接续道统之传必须有文献(“文字”)的依据,传道者是通过阐释上一代传道者所撰写的经典而得到领悟。于是,上一个传道者与下一个传道者之间虽然存在千余年历史间隔,但通过文献依据或师承渊源,历代传道者都被纳入了一种历史时间的序列或“经籍”的序列之中,从而使道统在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论证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客观的约束。
因此,《文化权力》尝试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质疑朱熹道统谱系的努力虽然未臻完善,但其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醒我们,在研究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客观的学统”并不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道统与学统”并非“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不可调和;相反,朱熹在肯定“心传道统”的前提下,形成了“因其语而得其心”的道统论述;而这一论述正是由客观性(历史性)与主观性(哲学性)两者有机统合而成的,不可偏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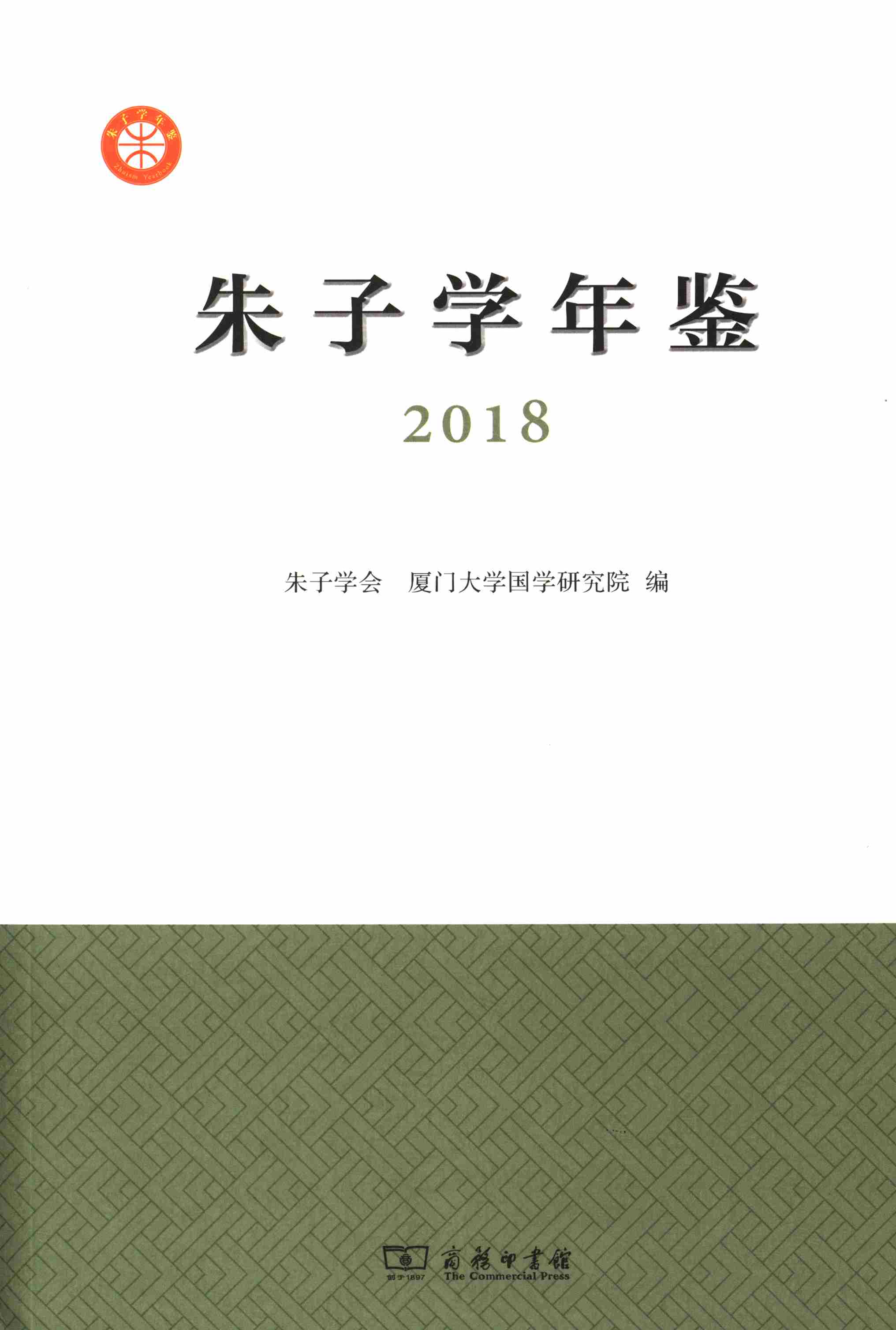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