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一、前言
宋明理学之兴起,其中朱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此因后续者,无论是宗朱或反朱,都多少与朱学相关;朱子继承程子之学而集大成,其编定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学者的必读之书[1],影响所及遍布东亚,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四书”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而朱子结合此四本书,并视此四者为道统的传承: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之后,汉儒无承继,此道统传跳而至程子,而朱子又是此道统的承继者,世称程朱理学。
朱子视自己是正统孟子的承继者,其《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孟子全文逐字逐句地一一注释。在朱子的年代,同时有象山兴起[2,象山属心学,而朱子属理学,双方批对方是禅学;朱子批象山教人不读书,沦为禅,而象山则批朱子求理于外,属义外,是告子之学,在“无极太极”之论辩时亦批朱子杂禅。二人所争辩的,则是谁人能够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真能承继孟子之学?
到了明代,阳明学兴起,亦是反对朱子的义外之说,视朱子格物穷理于外,非孟子的义内之学。阳明学的兴起,则是从其本身体证而来,原本视朱子为圣学的阳明,依于朱子之教而格竹子不得,最终于龙场体悟,发现格物致知原来不离于吾心,于是而有心学的倡议。阳明亦视己才是孟学继承人。此心学与理学的对抗,在《明儒学案》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两派都自认堪为孟学的正统。
本文主要比较朱子与阳明学的不同,并聚焦于二人于孟子性善论之诠解。朱子与阳明对孟子言“性”的见解不同,朱子继于程子,视性为“天理”,而认定孟子之论性而于气有所不备,“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3]。因为性只是理,于气上便有所不足,如朱子言:
《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4]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认为人性与物性于天理处相同,都是仁义礼智,但于气禀的分受不同,人能全其理,而物只能表现其部分。人性、物性皆善,因为都是理,只因气禀的不同而于气质之性上有少异,于是认定在这之中便要加入形气之说始足,而孟子本人则少了此气的转语。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5],一者为天地之性,此性即理,另一性乃此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人性与物性在天理处相同,但在气质之性上始有不同。
以上看出朱子有二性之说,并以性即理为提纲,视孟子的性善是即于天理的性,此性为仁义礼智之性;至于阳明的学说乃针对朱子学而起,朱子学的二元架构,阳明缝补之。朱子将工夫析分为二:先知后行,此知与行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朱子主张体用二元、形上形下二元,以及分判已发、未发为二,凡此,阳明皆一以贯之。[6]
至于“性”的议题,朱子视“性即理”,心可以具理,然心不是理;阳明却视心即性即理。阳明虽也有心即理之说,然而此心即理,是否绝于气呢?阳明视心即理即气,此心并不绝于气,同样地,阳明言性,亦是性即理即气。阳明的原文出处,后文详之。
于此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此一性为天地之性,此中只有理而无气,至于气质之性,为理落于气中所表现出的性,如月印万川,万川所倒映出的月亮,不如本来月亮之光明,此即理一分殊,天理落于形气中而为气质之性。至于阳明的性义,则是把朱子的二元论性义合而为一,以理与气之相合以言性。朱子视性即理,而阳明视性是理、气合,孰是孰非?在此将以孟子的原意来评论。[7]
二、朱子论性
朱子的二性之说始于程子,而朱子集大成而发扬理学,认定孟子于“气”有所不备,此指孟子于气讲得不足而需增补,于是朱子补了形下之气,此为气质、气禀,然此气与理不离不杂,性理与气的相加而为气质之性,乃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者。朱子于《论语》注“性相近,习相远”处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
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
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8]朱子认为,孔子所言“性相近”之性,乃气质之性,而非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有美恶之分,岂能言“相近”?美、恶之相反犹若冰与炭,但溯于其初,还是可谓相近。朱子的意思是,其初不甚相远;美恶者,于其初时并未相反若此。气质之性之所以相差甚多,乃后天之习染所造成,故朱子所言的气质之性,一方面指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另一方面,此气质之性与习相关。然依朱子后的学者,认为气质之性与习应该要做区分,而朱子未有区分,因为性是生而有之,习是后天习染,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两者是该区分。黄宗羲认为:
此章(富岁章)是“性相近习相远”注疏,孙淇澳先生曰:“今若说富岁凶岁,子弟降才有殊,说肥硗雨露人事不齐,而谓麰麦性不同,人谁肯信?至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就形生后说。若禀气于天,成形于地,受变于俗,正肥硗雨露人事类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谓习耳。今不知为习,而强系之性,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9]
黄宗羲注《孟子富岁子弟》章,引孙淇澳的见解,黄与孙两人认为性与习该做区分,性者生而有之,习者,后天也。而朱子把气质之性与习两者混在一起了。然而朱子论性,为何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从程子而来,程子的理由是“性即理”,性是仁义礼智,性之为体,体中也只有仁义礼智,此是性,也是天理,此天理在人,人人相同,不该言相近。而孔子何以言“性相近”?乃因为此处是就气质之性而言,非就本然之性言。故在程朱而言,天地之性,人人相同,都是天理;气质之性,则有美恶之不同,但在其初处,还是相近的。
于此看出朱子对于性的二层区分,有相同之性,此天地之性,性之本也,另一是气质之性,此性与气相混而成。朱子的二层区分,在注释《孟子》的《生之谓性》章处亦表现无遗: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10]
朱子认为,孟子言性是天理,此为形上,此性只有理而无形下之气。至于告子所言“生之谓性”,乃是天之气,而不是理,此为形下。而人物之生,亦有其形上之理,也有形下之气,因为理气不离不杂。此所谓的形上之理,人物皆有之,而人物之不同,在于气禀的差异,人能得其全,物得其偏,此偏、全者,就其能否实践道德之偏全而言,人能道义全具而能实践,动物道义亦全具,然气禀不佳而不能全之,只能表现其偏。
就其气言,人与物都有其知觉运动;就其理言,人物亦都有仁义礼智,但人能全之,物则不能。而人性之所以为无不善,为万物之灵者,乃在于人道义全具,故能付之实践以表现之,动物则只能表现其一部分,不及于人。而告子的差错在于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当之。可见朱子所认定的性可以有两层,上一层为天地之性,此性只有理,而无气,另一层是所谓气性,此气性,如告子所言,以气当之,所谓的生之谓性、食色之性,此所谓的中性材质义之性,而非无不善的本然之性。[11]
在朱子而言,《告子上》的前四章,告子所言之性皆只是形下的气性,未及于形上的必善之性;而于朱子所注的《告子上》前四章,并论及荀子、扬雄、佛氏、告子等人皆如此,所言之性皆是气性,而只有孟子论性是正确的,其视性善之性是形上之性,是天理,而其他人则皆误认气为性,只知饮食男女,而不及于道德。亦是说,荀子、告子等人只知于知觉运动的动物性,此动物性中不具道德性,唯有孟子能够指出道德性。虽人亦有动物性,然孟子不以动物性为性,虽不完全反对动物性,不反对好色、好货之心,然孟子心目中的性乃是以形上之理、道德性为主。
如果再看朱子于《性无善无不善》章所举者更为清楚。朱子举前人之言来做说明,其言: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
这里举了两段程子的话、一段张子的话,都认定性有二,一为天地之性,一为气质之性,而君子以天地之性为第一性,此乃性善之本。又程子之言表示,性与气二者要兼备始可。
然而,这是孟子的本意吗?孟子所言性若早已有气质于其中,则不消如程子一般,言性善若不补个气则为不备(程子先于性中脱落了气质,于是说孟子不备,又自行补上)。孟子的性善若早有气于其中,则不用如程子先把性中的气划分掉,然后说天地之性只有理而无气,因此有所不备,需要再补个气。若是阳明则于性中不脱落气,下文详之。
程子将性与气划分为二,论性,则只是理,而有不足,故要加气以补不足。至于第二段程子的说法,以性与才相比,此性即理,系出于天,而才禀于气,故其定义之才与孟子的才义不同。[13]程子的才是所谓的气禀、气质之性,故程子以性与才作为一相对待概念,其实也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区分。
从以上引文皆可看出,朱子论孟子性善区分了二性,亦可视为程朱理气论的变形,天地之性为理,而气质之性是理带有气。所谓天地之性之为理,亦可言之为理性,或是道德性,至于气质之性则指食色之性、生之谓性等。而朱子以二元区分来看待孟子之性论,阳明并不同意,下文明之。
三、阳明论性
若总结阳明之论孟子性善义,可谓性是理气合,一方面,阳明认为心即性即理,故“性即理”亦可接受,而另一方面,阳明言性又不只是理,尚且是气,故性为理气合。在《传习录·中卷》《答周道通书》有如下对话: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
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
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14]
周道通的疑惑是,程子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不知所指者何?其实,“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有人视为受有禅学“本来面目”影响,如黄宗羲即是如此;“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者,乃指本然之性,此系言语道断,如道之不可道;若一旦可说,则不是本然之性了,而是本然之性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故曰:“才说性已不是性。”一旦说性,则落为气质之性,而不是性之本然矣。而朱子认为,“不容说”者,指人尚未出生之际,尚未具体成为人的气质之性;而曰“不是性”者,乃因不是本然之性,而是本然之性杂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
上引文中,一方面是周道通的疑惑,一方面也是程朱的回答;于此见出,程朱都有两层性论的意思。至于阳明则不然,阳明面对朱子的二元区分,总是缝补之,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缝补;如朱子的工夫之诚明两进[15],阳明则以致良知之本体工夫一以贯之。如今朱子的二性之说,在阳明则以一性通贯之,主张心即性即理。
然而性之即于理,是否即于气?理者,可视为道德之谓;气者,可谓为食色之性等。阳明言生之谓性,生者就气言,所谓的生理欲望、饮食男女等,此语是告子所言,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又谓“食色性也”,而阳明认为此“生”字与气有关,故气即是性,性即是气。至于阳明之解程子“才说性已不是性”,是认为一旦说气即是性时,则仅谈到气性一边,而未有性理。亦是说,依于阳明之见,性即理即气,但若只强调气的一面,则偏于气,而不及理,故不是性之本源;但若只强调本源而不及气,亦不可。孟子之言性固然是从本源上说,乃视性即理,然性只有理而无及于气乎?人性中只有道德,而无形色饮食等乎?阳明也不认为如此,而是性即理即气,理为本,而气为辅,此才是性。
故阳明言性善须在气上始见得,离气也无所谓性。恻隐、羞恶等在阳明视之为气;在朱子也视之为气,是情。然朱子是理气二元,形上形下二元区分,而阳明是理气一滚,形上形下相连。既然阳明言性是理气一滚,又将如何解释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说?
其实这句话,是由朱子真正继承,而阳明也自许可以继承于北宋精神,故其认为有些人只认得性理的一边,而有些人只认得气性一边,这都有所不及。视性为理者,只见道德性,而排斥饮食男女、情感等;视性为气者,却不及于道德。所以最后阳明认为性即气,气即性,性中本有气,非如朱子的先以性即理而排斥了气,最后再补气质之性,把气加回来,而为气质之性。阳明之不同于朱子在于,阳明一开始便不把气排除在性之外,性中本有理、有气,理气相即而为性,性是理气合。于此可见阳明论性与朱子不同,朱子所谓的性善是只有理而无气,而阳明认定的性善是理气相合。
以上讨论了阳明与朱子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见解,以下以孟子原文为标准,视二人谁人得孟子之意。
四、孟子论性
以上二位大儒之相争,对于性的见解不同,然而谁人为正?其实二位儒者都是在诠释孟子的性善论,故以孟子为标准则可判定谁人合于孟子。若如此则必定要回到孟子原文中始可判别。至于一旦谈到孟子的原文时,不知觉地必涉及诠释,本文在此希望尽量少些个人之诠释,而让孟子原文、原意展现出来。接下来,可以先看孟子的《富岁》章: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孟子于此所言的性是什么?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也。”圣人有其人性,一般人也有人性,人与人之间未有不同,圣人能充尽之,一般人亦可充尽之,如同都是麦,若人事稼耕上,其土壤相同,培育时间上相同,则培养出来的结果便能相近。
孟子此章尚有两个重点,第一,孟子言“举相似”,虽孟子于此章亦言“相同”,如“同嗜焉”“同听焉”,但其所谓的相同,应该是相似的意思,如同孟子言“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足之相同,是指其相似,足的大小是相近的,而不会相同;同样的,人的口味亦是相近,而不是相同。
第二,孟子于此所言之性为何?孟子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犬马其性所好的口味,与人性的口味亦不相同,因其不同类所造成,牛好细草,而人则嗜炙,从于易牙之味。故在孟子而言,所谓的人性虽以仁义内在为人性,但人性不止于此,人性如同人这一类的本性,其口之于味者亦是性,故人性中有道德、有食色,此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纵是动物性中,人与动物亦不全同,人好西施,而物不好西施。[16]于此可见,人性中不只有道德性,而是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故孟子言:“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是指口之于味也是人的本性,乃因着运命气数之不齐,而不能必得之,于是君子视此则可有可无,不要求于必得之。
于此而知,阳明与朱子论性,阳明以性是理气合,较符合孟子,而朱子以性即理的看法,与孟子相去较远。朱子补回一个气质之性,也许可弥补此差别,然于本源处,认定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更无食色之性,一分一合之间,已是多此一举。
再举《食色性也》章为例,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如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
告子谈“食色性也”,亦谈“仁内义外”,至于孟子的回辩则只强调义者不在外,而是义内。谓仁内者,孟子也同意,至于食色性也,孟子亦无辩,不只无辩,而且在文末更以饮食来驳告子,看出孟子并不反对食色之性。
整篇论旨,告子视义为外,而孟子视义为内。然而告子所言外者,以义者为外,指道德的当宜者在于外,所谓的“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指的是长者为外在,而不是我能决定的;而孟子认为长之者才是义,非以长者为义,故视为内。何者为内呢?内是指吾人所生而有之者,在于我身上。仁何以是内?乃因仁是爱人,爱人从爱亲开始,故秦人之弟不爱,而吾弟则爱,此亲情血缘之关系,而为内,故仁之为内,孟子、告子都能同意。
至于义者,孟子视之为内,而告子视之为外,因为孟子视长之者为义;而告子视长者为义,因“彼长而我长之”,故彼长者,非于我也,是外在的。而孟子视仁义礼智为内,为性,是生而有之,内在本有的。然孟子论性善为内,为固有、本有,并不只有仁义是本有,而且人性中除了仁义之性外,亦有食色之性,告子承认了食色之性,故孟子以饮食之嗜炙以喻之。[17]内者,本有也,亦是人性,人性中有仁义,亦有动物性的饮食与生理欲望,只是人的饮食与动物的饮食亦不甚相同。人所喜好的是易牙所煮之食,人喜好的是烧烤之炙。而告子于论辩中,以秦人之弟则不爱,以仁为内,而爱自己兄弟;而以长楚人之长,亦长吾家之长,以长为悦,此悦不在我,而在对象,与吾弟之爱为血缘者不同。血缘是内在者故为内,有血缘者则爱,无血缘者则不爱。至于义,则无关于血缘与否,则以外在的长或不长为标准,故告子视之为外。
孟子最后只好举出人性中的饮食亦为内,亦是人性的一环以回辩,无论嗜谁人所做之炙,都喜欢,且此之爱炙者不从外来,而且是生而有之,是人这一类特殊的饮食习惯。亦是说告子认义为外,而孟子以饮食为内以辩之,论辩义内或外者,为何与饮食有关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此“内”的意思就“性”而言,乃生而有之,人性生而有仁义,亦有特殊饮食性,故孟子以此折服了告子。这也说明,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食色,则性是理气混,而以阳明的意思近于孟子。若于人性中把道德性与饮食切割开来,则孟子此章变得不知所云,而之所以有意义,乃在于人性中,道德与饮食男女者皆于其中。
或可再参见《孟子·告子上》的另一章有着相同的义理,孟季子与公都子的对话代表着孟子与告子的对话,其曰: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此场景同于上一章孟子与告子的义内、义外之辩,而如今场景换为学生的论辩,背后所代表者,则是双方的师承即孟子与告子的见解。孟季子的意思,无论是敬弟、敬叔父,或是敬兄、敬乡人,都由外在位置决定,此为外而不为内,这与“彼长而我长之”的意思一样,乃是告子的义外之说,指的是道义的标准为外在所决定,非我内在之决定。外在决定者,之所以敬叔父者,因叔父年纪长,而敬叔父;敬弟者,乃因尸位之故,此皆为外在决定。但孟子的意思是,长之者才是义,而非长者为义,义是愿意恭敬之心,是在我而不在外。最后的论辩,因着公都子之说而折服了孟季子,此公都子亦是承于孟子的精神而来。
此章与上一章如出一辙,谈义内、义外的问题,最后都以饮食之内在而折服对方。表示人性中,仁义内在,此为人性,然人性之内在者,不只是仁义,饮食亦为内在。此饮食之为内在,为告子、孟季子所深知,故告子言:“食色性也。”而且最后孟子以饮食之内在,来证成了仁义亦内在,仁义与饮食,都是人性。如此才足以折服告子、孟季子。此都说明孟子论性中包括了道德与食色。
然孟子亦不反对食色之性,此为内在,何以孟子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章谈到: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孟子对于“生之谓性”的反对,乃因这是以“生”来定义“性”(“性”者,生也),然性是落实于类上的殊义,乃落于此类而为此类之本质,足以区别于他类者,而生则是存活、存在义,范畴较“性”义大得多,故两者不应做比配。白羽、白雪、白玉之白者,是共相;而犬性、牛性、人性,是殊相,三性都不同,不可以共相定义殊相。白羽、白雪、白玉者,如同所谓的“生”,是为共相范畴,都就其白色而提出共相;而生者,都就其存在而言其共相,万物皆生。至于性,则有其分殊性,故万物之性不同,不可浑沦无别于人性、牛性与犬性,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犬性亦不同,人能实践道德,人性善,动物则无,人的饮食之性与牛的饮食亦不同。此乃“生之谓性章”的义理。孟子并不是反对形下气质之性,而是认为“生”与“性”之间关系的不对等,不可混而同之,更不可以生定义性。
除此之外,孟子亦言“形色天性”[18],乃是指人性中道德是为人性,饮食亦是,人的形色亦与他类不同。故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饮食之特殊性,有其身体与他类之不同。人的形色与动物的形色不同,此为天性所赋予。
然而,孟子既然以人性中的饮食为重要,为何又要批评饮食?亦视耳目为小体?孟子对饮食之人曾有批评,原文如下: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
饮食之人而为人所贱者,因其养小而害大,若饮食作为养小而培育大,则饮食也不当被轻贱。所谓大者,大体也,心官也;小者,小体也,耳目之官也。耳目之官不需被反对,耳目之官是在不思而蔽于物时才有恶。恶是习所造成(也是从于小体所造成,此从者,心官从之)[19],本该性善,形色天性皆为善,耳目之善乃能听从于大体而做善事,如今因蔽于物,为习所染,故有恶,而恶者非耳目之官所该负责,而是蔽于物所造成,是习染所带坏,即因此心官不思而接受恶的习染所致。所以孟子此段最后言:“饮食之人,无有失也。”若饮食之人无失,无以小害大,则饮食之滋养却是应当的。孟子亦饮食,唯其饮食不以小害大,大者,心官之思诚而有德,而饮食正好用以照顾身体,用以实践道德,不妨害大者。饮食、食色者,亦是人性的一环,不可偏废。
面对齐宣王所言“寡人好色、好货”等弊病,孟子的回答是:“于王何有?”其认为好色又何妨,有此则能有其同理心。人这一类的人性就有其人性上的生理需求,此生理需求亦不同于动物,人好西施,动物则不好。于此好色处指点其为人性,则百姓亦为人,亦有人性,则亦需要结婚,故孟子指点若能推己及人,以同理心体会民心,则能行王道,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由此人性而能推己及人,透过小体用以实践大体。
形色都是睟面盎背的表现,形色即于天性,天性中的道德因着食色而能养,而能表现,此即孟子性善论之正义。性者,身体与道德都结合于其中,理气合于其中。若如此诠释孟子的性论,则可知,朱子、阳明对于人性见解的比较,则阳明以性是为理气合的说法较合于孟子,至于朱子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掉,而说孟子不备于气,然后又帮孟子补一个气质之性,可谓多此一举,虽无大错,然一分一合之间,性义枯矣。
五、结语与反思
本文讨论孟子的性义,以及朱子与阳明二人相关诠释何者较合。朱子与阳明常都用自己的体系套于经典,迁就古人以合于自己,可谓“六经”皆我脚注!而本文在此只谈孟子的性义,其他省略。文中谈到,朱子视性即理,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悌,更无食色之性,而阳明认为性是理与气的结合(船山也认为性是理气合)。此理者,道德性也,气者,形色也,食色也。而最后判之以孟子原文,以评二人谁能较得孟子原意。文中举了《孟子·告子上》诸章为论证。本文认为,孟子所言性不是只有道德性,也包括食色之性,也包括形色天性,这些都善,动物亦有形色,然不能助之以成就道德,故动物身体亦无所谓善,而人的形色可成就德性,亦为天性,亦为善。而朱子却视性即理,把气质部分去除,阳明则未去除,故阳明得之,朱子未得之。
本文认为,孟子论性之义,为阳明较能合之。朱子之所以认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此有其时代的需求,一方面,需面对当时时代的需要,如魏晋所发展的才性之学、佛学的无明习之说,另一方面,也结合了佛学的贬低食色的见解,然此应非孟子本意。再者,朱子的二性之说也不合于孟子,孟子未有二性之说。又朱子言性,视人性、物性皆可为善,这也是创造性的诠释,孟子的性善是指人性善,犬牛则无,犬牛虽无善,但犬性还是不同于牛性,非可把此二性泛同之。朱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与物的区别是成就道德的全与偏之区别,此亦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朱子对于习的说明太少,系以气质之性言之,无论先天、后天都以气质之性来定义,然性既是生而有之,则与习应有区别,此朱子浑沦之处。
然朱子亦非全错,只是他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除,而后再补气质之性回去,此分合之际,实是多此一举,而性亦枯槁矣。依于原文,孟子其实并未太多反对饮食男女,而是反对不依大体的饮食男女、以小害大的饮食男女,若饮食得其正者,孟子亦正视之,口之于味亦是性,形色亦是天性,此儒家对于食色之看法,而与佛家有别,不用贬低饮食男女之事,只要得正则可。
宋明理学之兴起,其中朱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此因后续者,无论是宗朱或反朱,都多少与朱学相关;朱子继承程子之学而集大成,其编定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学者的必读之书[1],影响所及遍布东亚,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四书”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而朱子结合此四本书,并视此四者为道统的传承: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之后,汉儒无承继,此道统传跳而至程子,而朱子又是此道统的承继者,世称程朱理学。
朱子视自己是正统孟子的承继者,其《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孟子全文逐字逐句地一一注释。在朱子的年代,同时有象山兴起[2,象山属心学,而朱子属理学,双方批对方是禅学;朱子批象山教人不读书,沦为禅,而象山则批朱子求理于外,属义外,是告子之学,在“无极太极”之论辩时亦批朱子杂禅。二人所争辩的,则是谁人能够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真能承继孟子之学?
到了明代,阳明学兴起,亦是反对朱子的义外之说,视朱子格物穷理于外,非孟子的义内之学。阳明学的兴起,则是从其本身体证而来,原本视朱子为圣学的阳明,依于朱子之教而格竹子不得,最终于龙场体悟,发现格物致知原来不离于吾心,于是而有心学的倡议。阳明亦视己才是孟学继承人。此心学与理学的对抗,在《明儒学案》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两派都自认堪为孟学的正统。
本文主要比较朱子与阳明学的不同,并聚焦于二人于孟子性善论之诠解。朱子与阳明对孟子言“性”的见解不同,朱子继于程子,视性为“天理”,而认定孟子之论性而于气有所不备,“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3]。因为性只是理,于气上便有所不足,如朱子言:
《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4]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认为人性与物性于天理处相同,都是仁义礼智,但于气禀的分受不同,人能全其理,而物只能表现其部分。人性、物性皆善,因为都是理,只因气禀的不同而于气质之性上有少异,于是认定在这之中便要加入形气之说始足,而孟子本人则少了此气的转语。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5],一者为天地之性,此性即理,另一性乃此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人性与物性在天理处相同,但在气质之性上始有不同。
以上看出朱子有二性之说,并以性即理为提纲,视孟子的性善是即于天理的性,此性为仁义礼智之性;至于阳明的学说乃针对朱子学而起,朱子学的二元架构,阳明缝补之。朱子将工夫析分为二:先知后行,此知与行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朱子主张体用二元、形上形下二元,以及分判已发、未发为二,凡此,阳明皆一以贯之。[6]
至于“性”的议题,朱子视“性即理”,心可以具理,然心不是理;阳明却视心即性即理。阳明虽也有心即理之说,然而此心即理,是否绝于气呢?阳明视心即理即气,此心并不绝于气,同样地,阳明言性,亦是性即理即气。阳明的原文出处,后文详之。
于此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此一性为天地之性,此中只有理而无气,至于气质之性,为理落于气中所表现出的性,如月印万川,万川所倒映出的月亮,不如本来月亮之光明,此即理一分殊,天理落于形气中而为气质之性。至于阳明的性义,则是把朱子的二元论性义合而为一,以理与气之相合以言性。朱子视性即理,而阳明视性是理、气合,孰是孰非?在此将以孟子的原意来评论。[7]
二、朱子论性
朱子的二性之说始于程子,而朱子集大成而发扬理学,认定孟子于“气”有所不备,此指孟子于气讲得不足而需增补,于是朱子补了形下之气,此为气质、气禀,然此气与理不离不杂,性理与气的相加而为气质之性,乃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者。朱子于《论语》注“性相近,习相远”处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
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
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8]朱子认为,孔子所言“性相近”之性,乃气质之性,而非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有美恶之分,岂能言“相近”?美、恶之相反犹若冰与炭,但溯于其初,还是可谓相近。朱子的意思是,其初不甚相远;美恶者,于其初时并未相反若此。气质之性之所以相差甚多,乃后天之习染所造成,故朱子所言的气质之性,一方面指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另一方面,此气质之性与习相关。然依朱子后的学者,认为气质之性与习应该要做区分,而朱子未有区分,因为性是生而有之,习是后天习染,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两者是该区分。黄宗羲认为:
此章(富岁章)是“性相近习相远”注疏,孙淇澳先生曰:“今若说富岁凶岁,子弟降才有殊,说肥硗雨露人事不齐,而谓麰麦性不同,人谁肯信?至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就形生后说。若禀气于天,成形于地,受变于俗,正肥硗雨露人事类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谓习耳。今不知为习,而强系之性,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9]
黄宗羲注《孟子富岁子弟》章,引孙淇澳的见解,黄与孙两人认为性与习该做区分,性者生而有之,习者,后天也。而朱子把气质之性与习两者混在一起了。然而朱子论性,为何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从程子而来,程子的理由是“性即理”,性是仁义礼智,性之为体,体中也只有仁义礼智,此是性,也是天理,此天理在人,人人相同,不该言相近。而孔子何以言“性相近”?乃因为此处是就气质之性而言,非就本然之性言。故在程朱而言,天地之性,人人相同,都是天理;气质之性,则有美恶之不同,但在其初处,还是相近的。
于此看出朱子对于性的二层区分,有相同之性,此天地之性,性之本也,另一是气质之性,此性与气相混而成。朱子的二层区分,在注释《孟子》的《生之谓性》章处亦表现无遗: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10]
朱子认为,孟子言性是天理,此为形上,此性只有理而无形下之气。至于告子所言“生之谓性”,乃是天之气,而不是理,此为形下。而人物之生,亦有其形上之理,也有形下之气,因为理气不离不杂。此所谓的形上之理,人物皆有之,而人物之不同,在于气禀的差异,人能得其全,物得其偏,此偏、全者,就其能否实践道德之偏全而言,人能道义全具而能实践,动物道义亦全具,然气禀不佳而不能全之,只能表现其偏。
就其气言,人与物都有其知觉运动;就其理言,人物亦都有仁义礼智,但人能全之,物则不能。而人性之所以为无不善,为万物之灵者,乃在于人道义全具,故能付之实践以表现之,动物则只能表现其一部分,不及于人。而告子的差错在于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当之。可见朱子所认定的性可以有两层,上一层为天地之性,此性只有理,而无气,另一层是所谓气性,此气性,如告子所言,以气当之,所谓的生之谓性、食色之性,此所谓的中性材质义之性,而非无不善的本然之性。[11]
在朱子而言,《告子上》的前四章,告子所言之性皆只是形下的气性,未及于形上的必善之性;而于朱子所注的《告子上》前四章,并论及荀子、扬雄、佛氏、告子等人皆如此,所言之性皆是气性,而只有孟子论性是正确的,其视性善之性是形上之性,是天理,而其他人则皆误认气为性,只知饮食男女,而不及于道德。亦是说,荀子、告子等人只知于知觉运动的动物性,此动物性中不具道德性,唯有孟子能够指出道德性。虽人亦有动物性,然孟子不以动物性为性,虽不完全反对动物性,不反对好色、好货之心,然孟子心目中的性乃是以形上之理、道德性为主。
如果再看朱子于《性无善无不善》章所举者更为清楚。朱子举前人之言来做说明,其言: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
这里举了两段程子的话、一段张子的话,都认定性有二,一为天地之性,一为气质之性,而君子以天地之性为第一性,此乃性善之本。又程子之言表示,性与气二者要兼备始可。
然而,这是孟子的本意吗?孟子所言性若早已有气质于其中,则不消如程子一般,言性善若不补个气则为不备(程子先于性中脱落了气质,于是说孟子不备,又自行补上)。孟子的性善若早有气于其中,则不用如程子先把性中的气划分掉,然后说天地之性只有理而无气,因此有所不备,需要再补个气。若是阳明则于性中不脱落气,下文详之。
程子将性与气划分为二,论性,则只是理,而有不足,故要加气以补不足。至于第二段程子的说法,以性与才相比,此性即理,系出于天,而才禀于气,故其定义之才与孟子的才义不同。[13]程子的才是所谓的气禀、气质之性,故程子以性与才作为一相对待概念,其实也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区分。
从以上引文皆可看出,朱子论孟子性善区分了二性,亦可视为程朱理气论的变形,天地之性为理,而气质之性是理带有气。所谓天地之性之为理,亦可言之为理性,或是道德性,至于气质之性则指食色之性、生之谓性等。而朱子以二元区分来看待孟子之性论,阳明并不同意,下文明之。
三、阳明论性
若总结阳明之论孟子性善义,可谓性是理气合,一方面,阳明认为心即性即理,故“性即理”亦可接受,而另一方面,阳明言性又不只是理,尚且是气,故性为理气合。在《传习录·中卷》《答周道通书》有如下对话: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
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
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14]
周道通的疑惑是,程子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不知所指者何?其实,“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有人视为受有禅学“本来面目”影响,如黄宗羲即是如此;“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者,乃指本然之性,此系言语道断,如道之不可道;若一旦可说,则不是本然之性了,而是本然之性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故曰:“才说性已不是性。”一旦说性,则落为气质之性,而不是性之本然矣。而朱子认为,“不容说”者,指人尚未出生之际,尚未具体成为人的气质之性;而曰“不是性”者,乃因不是本然之性,而是本然之性杂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
上引文中,一方面是周道通的疑惑,一方面也是程朱的回答;于此见出,程朱都有两层性论的意思。至于阳明则不然,阳明面对朱子的二元区分,总是缝补之,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缝补;如朱子的工夫之诚明两进[15],阳明则以致良知之本体工夫一以贯之。如今朱子的二性之说,在阳明则以一性通贯之,主张心即性即理。
然而性之即于理,是否即于气?理者,可视为道德之谓;气者,可谓为食色之性等。阳明言生之谓性,生者就气言,所谓的生理欲望、饮食男女等,此语是告子所言,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又谓“食色性也”,而阳明认为此“生”字与气有关,故气即是性,性即是气。至于阳明之解程子“才说性已不是性”,是认为一旦说气即是性时,则仅谈到气性一边,而未有性理。亦是说,依于阳明之见,性即理即气,但若只强调气的一面,则偏于气,而不及理,故不是性之本源;但若只强调本源而不及气,亦不可。孟子之言性固然是从本源上说,乃视性即理,然性只有理而无及于气乎?人性中只有道德,而无形色饮食等乎?阳明也不认为如此,而是性即理即气,理为本,而气为辅,此才是性。
故阳明言性善须在气上始见得,离气也无所谓性。恻隐、羞恶等在阳明视之为气;在朱子也视之为气,是情。然朱子是理气二元,形上形下二元区分,而阳明是理气一滚,形上形下相连。既然阳明言性是理气一滚,又将如何解释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说?
其实这句话,是由朱子真正继承,而阳明也自许可以继承于北宋精神,故其认为有些人只认得性理的一边,而有些人只认得气性一边,这都有所不及。视性为理者,只见道德性,而排斥饮食男女、情感等;视性为气者,却不及于道德。所以最后阳明认为性即气,气即性,性中本有气,非如朱子的先以性即理而排斥了气,最后再补气质之性,把气加回来,而为气质之性。阳明之不同于朱子在于,阳明一开始便不把气排除在性之外,性中本有理、有气,理气相即而为性,性是理气合。于此可见阳明论性与朱子不同,朱子所谓的性善是只有理而无气,而阳明认定的性善是理气相合。
以上讨论了阳明与朱子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见解,以下以孟子原文为标准,视二人谁人得孟子之意。
四、孟子论性
以上二位大儒之相争,对于性的见解不同,然而谁人为正?其实二位儒者都是在诠释孟子的性善论,故以孟子为标准则可判定谁人合于孟子。若如此则必定要回到孟子原文中始可判别。至于一旦谈到孟子的原文时,不知觉地必涉及诠释,本文在此希望尽量少些个人之诠释,而让孟子原文、原意展现出来。接下来,可以先看孟子的《富岁》章: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孟子于此所言的性是什么?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也。”圣人有其人性,一般人也有人性,人与人之间未有不同,圣人能充尽之,一般人亦可充尽之,如同都是麦,若人事稼耕上,其土壤相同,培育时间上相同,则培养出来的结果便能相近。
孟子此章尚有两个重点,第一,孟子言“举相似”,虽孟子于此章亦言“相同”,如“同嗜焉”“同听焉”,但其所谓的相同,应该是相似的意思,如同孟子言“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足之相同,是指其相似,足的大小是相近的,而不会相同;同样的,人的口味亦是相近,而不是相同。
第二,孟子于此所言之性为何?孟子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犬马其性所好的口味,与人性的口味亦不相同,因其不同类所造成,牛好细草,而人则嗜炙,从于易牙之味。故在孟子而言,所谓的人性虽以仁义内在为人性,但人性不止于此,人性如同人这一类的本性,其口之于味者亦是性,故人性中有道德、有食色,此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纵是动物性中,人与动物亦不全同,人好西施,而物不好西施。[16]于此可见,人性中不只有道德性,而是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故孟子言:“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是指口之于味也是人的本性,乃因着运命气数之不齐,而不能必得之,于是君子视此则可有可无,不要求于必得之。
于此而知,阳明与朱子论性,阳明以性是理气合,较符合孟子,而朱子以性即理的看法,与孟子相去较远。朱子补回一个气质之性,也许可弥补此差别,然于本源处,认定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更无食色之性,一分一合之间,已是多此一举。
再举《食色性也》章为例,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如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
告子谈“食色性也”,亦谈“仁内义外”,至于孟子的回辩则只强调义者不在外,而是义内。谓仁内者,孟子也同意,至于食色性也,孟子亦无辩,不只无辩,而且在文末更以饮食来驳告子,看出孟子并不反对食色之性。
整篇论旨,告子视义为外,而孟子视义为内。然而告子所言外者,以义者为外,指道德的当宜者在于外,所谓的“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指的是长者为外在,而不是我能决定的;而孟子认为长之者才是义,非以长者为义,故视为内。何者为内呢?内是指吾人所生而有之者,在于我身上。仁何以是内?乃因仁是爱人,爱人从爱亲开始,故秦人之弟不爱,而吾弟则爱,此亲情血缘之关系,而为内,故仁之为内,孟子、告子都能同意。
至于义者,孟子视之为内,而告子视之为外,因为孟子视长之者为义;而告子视长者为义,因“彼长而我长之”,故彼长者,非于我也,是外在的。而孟子视仁义礼智为内,为性,是生而有之,内在本有的。然孟子论性善为内,为固有、本有,并不只有仁义是本有,而且人性中除了仁义之性外,亦有食色之性,告子承认了食色之性,故孟子以饮食之嗜炙以喻之。[17]内者,本有也,亦是人性,人性中有仁义,亦有动物性的饮食与生理欲望,只是人的饮食与动物的饮食亦不甚相同。人所喜好的是易牙所煮之食,人喜好的是烧烤之炙。而告子于论辩中,以秦人之弟则不爱,以仁为内,而爱自己兄弟;而以长楚人之长,亦长吾家之长,以长为悦,此悦不在我,而在对象,与吾弟之爱为血缘者不同。血缘是内在者故为内,有血缘者则爱,无血缘者则不爱。至于义,则无关于血缘与否,则以外在的长或不长为标准,故告子视之为外。
孟子最后只好举出人性中的饮食亦为内,亦是人性的一环以回辩,无论嗜谁人所做之炙,都喜欢,且此之爱炙者不从外来,而且是生而有之,是人这一类特殊的饮食习惯。亦是说告子认义为外,而孟子以饮食为内以辩之,论辩义内或外者,为何与饮食有关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此“内”的意思就“性”而言,乃生而有之,人性生而有仁义,亦有特殊饮食性,故孟子以此折服了告子。这也说明,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食色,则性是理气混,而以阳明的意思近于孟子。若于人性中把道德性与饮食切割开来,则孟子此章变得不知所云,而之所以有意义,乃在于人性中,道德与饮食男女者皆于其中。
或可再参见《孟子·告子上》的另一章有着相同的义理,孟季子与公都子的对话代表着孟子与告子的对话,其曰: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此场景同于上一章孟子与告子的义内、义外之辩,而如今场景换为学生的论辩,背后所代表者,则是双方的师承即孟子与告子的见解。孟季子的意思,无论是敬弟、敬叔父,或是敬兄、敬乡人,都由外在位置决定,此为外而不为内,这与“彼长而我长之”的意思一样,乃是告子的义外之说,指的是道义的标准为外在所决定,非我内在之决定。外在决定者,之所以敬叔父者,因叔父年纪长,而敬叔父;敬弟者,乃因尸位之故,此皆为外在决定。但孟子的意思是,长之者才是义,而非长者为义,义是愿意恭敬之心,是在我而不在外。最后的论辩,因着公都子之说而折服了孟季子,此公都子亦是承于孟子的精神而来。
此章与上一章如出一辙,谈义内、义外的问题,最后都以饮食之内在而折服对方。表示人性中,仁义内在,此为人性,然人性之内在者,不只是仁义,饮食亦为内在。此饮食之为内在,为告子、孟季子所深知,故告子言:“食色性也。”而且最后孟子以饮食之内在,来证成了仁义亦内在,仁义与饮食,都是人性。如此才足以折服告子、孟季子。此都说明孟子论性中包括了道德与食色。
然孟子亦不反对食色之性,此为内在,何以孟子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章谈到: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孟子对于“生之谓性”的反对,乃因这是以“生”来定义“性”(“性”者,生也),然性是落实于类上的殊义,乃落于此类而为此类之本质,足以区别于他类者,而生则是存活、存在义,范畴较“性”义大得多,故两者不应做比配。白羽、白雪、白玉之白者,是共相;而犬性、牛性、人性,是殊相,三性都不同,不可以共相定义殊相。白羽、白雪、白玉者,如同所谓的“生”,是为共相范畴,都就其白色而提出共相;而生者,都就其存在而言其共相,万物皆生。至于性,则有其分殊性,故万物之性不同,不可浑沦无别于人性、牛性与犬性,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犬性亦不同,人能实践道德,人性善,动物则无,人的饮食之性与牛的饮食亦不同。此乃“生之谓性章”的义理。孟子并不是反对形下气质之性,而是认为“生”与“性”之间关系的不对等,不可混而同之,更不可以生定义性。
除此之外,孟子亦言“形色天性”[18],乃是指人性中道德是为人性,饮食亦是,人的形色亦与他类不同。故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饮食之特殊性,有其身体与他类之不同。人的形色与动物的形色不同,此为天性所赋予。
然而,孟子既然以人性中的饮食为重要,为何又要批评饮食?亦视耳目为小体?孟子对饮食之人曾有批评,原文如下: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
饮食之人而为人所贱者,因其养小而害大,若饮食作为养小而培育大,则饮食也不当被轻贱。所谓大者,大体也,心官也;小者,小体也,耳目之官也。耳目之官不需被反对,耳目之官是在不思而蔽于物时才有恶。恶是习所造成(也是从于小体所造成,此从者,心官从之)[19],本该性善,形色天性皆为善,耳目之善乃能听从于大体而做善事,如今因蔽于物,为习所染,故有恶,而恶者非耳目之官所该负责,而是蔽于物所造成,是习染所带坏,即因此心官不思而接受恶的习染所致。所以孟子此段最后言:“饮食之人,无有失也。”若饮食之人无失,无以小害大,则饮食之滋养却是应当的。孟子亦饮食,唯其饮食不以小害大,大者,心官之思诚而有德,而饮食正好用以照顾身体,用以实践道德,不妨害大者。饮食、食色者,亦是人性的一环,不可偏废。
面对齐宣王所言“寡人好色、好货”等弊病,孟子的回答是:“于王何有?”其认为好色又何妨,有此则能有其同理心。人这一类的人性就有其人性上的生理需求,此生理需求亦不同于动物,人好西施,动物则不好。于此好色处指点其为人性,则百姓亦为人,亦有人性,则亦需要结婚,故孟子指点若能推己及人,以同理心体会民心,则能行王道,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由此人性而能推己及人,透过小体用以实践大体。
形色都是睟面盎背的表现,形色即于天性,天性中的道德因着食色而能养,而能表现,此即孟子性善论之正义。性者,身体与道德都结合于其中,理气合于其中。若如此诠释孟子的性论,则可知,朱子、阳明对于人性见解的比较,则阳明以性是为理气合的说法较合于孟子,至于朱子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掉,而说孟子不备于气,然后又帮孟子补一个气质之性,可谓多此一举,虽无大错,然一分一合之间,性义枯矣。
五、结语与反思
本文讨论孟子的性义,以及朱子与阳明二人相关诠释何者较合。朱子与阳明常都用自己的体系套于经典,迁就古人以合于自己,可谓“六经”皆我脚注!而本文在此只谈孟子的性义,其他省略。文中谈到,朱子视性即理,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悌,更无食色之性,而阳明认为性是理与气的结合(船山也认为性是理气合)。此理者,道德性也,气者,形色也,食色也。而最后判之以孟子原文,以评二人谁能较得孟子原意。文中举了《孟子·告子上》诸章为论证。本文认为,孟子所言性不是只有道德性,也包括食色之性,也包括形色天性,这些都善,动物亦有形色,然不能助之以成就道德,故动物身体亦无所谓善,而人的形色可成就德性,亦为天性,亦为善。而朱子却视性即理,把气质部分去除,阳明则未去除,故阳明得之,朱子未得之。
本文认为,孟子论性之义,为阳明较能合之。朱子之所以认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此有其时代的需求,一方面,需面对当时时代的需要,如魏晋所发展的才性之学、佛学的无明习之说,另一方面,也结合了佛学的贬低食色的见解,然此应非孟子本意。再者,朱子的二性之说也不合于孟子,孟子未有二性之说。又朱子言性,视人性、物性皆可为善,这也是创造性的诠释,孟子的性善是指人性善,犬牛则无,犬牛虽无善,但犬性还是不同于牛性,非可把此二性泛同之。朱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与物的区别是成就道德的全与偏之区别,此亦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朱子对于习的说明太少,系以气质之性言之,无论先天、后天都以气质之性来定义,然性既是生而有之,则与习应有区别,此朱子浑沦之处。
然朱子亦非全错,只是他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除,而后再补气质之性回去,此分合之际,实是多此一举,而性亦枯槁矣。依于原文,孟子其实并未太多反对饮食男女,而是反对不依大体的饮食男女、以小害大的饮食男女,若饮食得其正者,孟子亦正视之,口之于味亦是性,形色亦是天性,此儒家对于食色之看法,而与佛家有别,不用贬低饮食男女之事,只要得正则可。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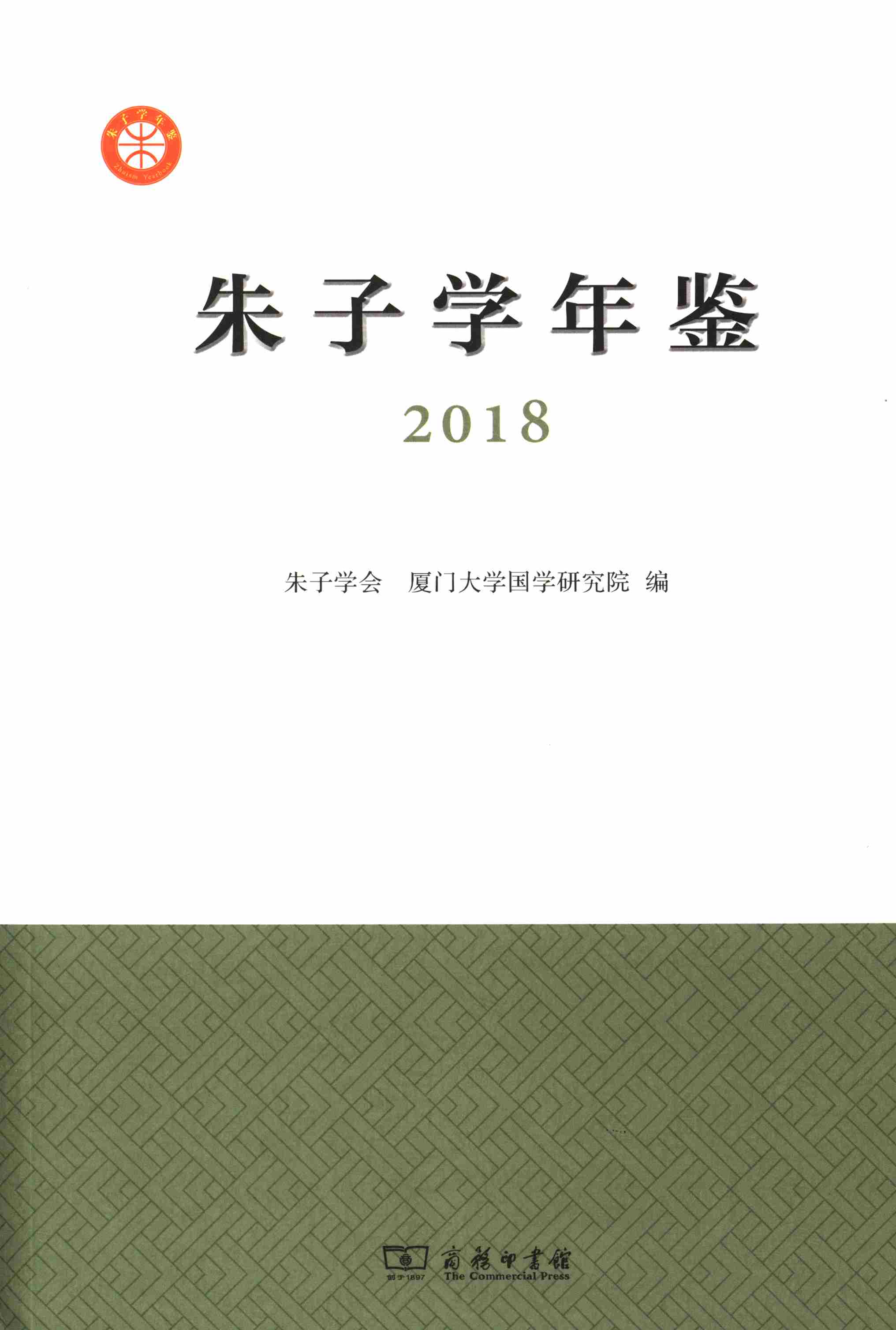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