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诠释及其意义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8)》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300 |
| 颗粒名称: | 朱熹对《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诠释及其意义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73-083 |
| 摘要: | 对于《论语·述而》中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杨伯峻将其解释为只要主动给他一点见面薄礼,就没有不教诲的;钱穆将其解释为干脯作为礼物;李泽厚则将其解释为十五岁以上的年龄。而宋代朱熹的解读较为特别,他将“束修”诠释为心,表达了人的内心修养的重要性。 |
| 关键词: | 《论语·述而》 自行束修 诠释 |
内容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此,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并将孔子所言解读为:“只要是主动地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从没有不教诲的。”[1]钱穆《论语新解》说:“束修:一解,修是干脯,十脡为束。古人相见,必执贽为礼,束修乃贽之薄者。又一解,束修谓束带修饰。古人年十五,可自束带修饰以见外傅。又曰:束修,指束身修行言。今从前一解。”[2]显然,钱穆把“束修”解读为“干脯”,类似于杨伯峻。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不同意将“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而是解读为“年十五以上”,并且认为,这种解读与孔子所讲“十有五而志于学”、《书传》“十五入小学”相应。为此,他把孔子所言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3]显然,这一解读,与杨伯峻、钱穆相去甚远。宋代朱熹《论语集注》把“束修”解读为肉脯,但不只是“见面薄礼”,把“束修”诠释为“心”,表达为心意,其中蕴含了许多合理的思想,可以为今人的解读和研究提供启迪。
一、束修:是“礼”还是“十五岁以上”
对于《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西汉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4]孔安国只是讲到“奉礼”而需要“束修”,并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进一步解读。孔安国还在注《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时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伎艺,其心休休焉。”[5]也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解读。
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但是其《论语郑氏注》大约于宋初开始失传。近年来,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研究有较大进展。有学者以《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塔那184号墓72TAM184:18/7(b),18/8(b)《论语郑氏注》之《述而》篇第9、10行为底本,并且结合敦煌文献,认为唐写本郑玄注的原文应该是:“自(始)行束修,谓年十五之时(奉?)酒脯。十五已上有恩好者以施遗焉。”[6]“束修”对应的是“酒脯”。郑玄还在讲到亲朋好友结婚、自己有事而无法前往需要遣人送礼时,说:“其礼盖壶酒、束修若犬也。”孔颖达疏曰:“礼物用壶酒及束修。束修,十脡脯也。若无脯,则壶酒及一犬。”[7]显然,在郑玄那里,“束修”是一种与“酒脯”有关的礼物。
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曰:“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应者也。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贽,至也,表已来至也。上则人君用玉,中则卿羔、大夫雁、士雉,下则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其中或束修、壶酒、一犬,悉不得无也。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贽,行束修以上来见谒者,则我未尝不教诲之。故江熙云:‘见其翘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贽见。修,脯也。孔注虽不云修是脯,而意亦不得离脯也。’”[8]显然,皇侃把“束修”解读为“十束脯”,并且还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与“脯”有关。该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孔颖达虽然在《礼记正义》中说“束修,十脡脯也”,但在《尚书正义》中疏孔安国“如有束修一介臣”时,却说:“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节,此亦当然。”[9]他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为“束带修节”。
南北朝范晔撰《后汉书》,唐代李贤等为之作注。其中注《伏湛传》“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曰:“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10]又注《延笃传》“且吾自束修以来”,曰:“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1]在这里,李贤既讲“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又讲“束修谓束带修饰”,应当是指年十五以上自行束修,“束带修饰”。因此,“束修”是就“束带修饰”而言,而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可见,汉唐时期诸儒解读“束修”,既有如郑玄解读为与“酒脯”有关的礼物,或皇侃解读为“脯”,也有如李贤解读为“束带修饰”,虽然郑玄、李贤的解读与“年十五以上”有关,但都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李泽厚《论语今读》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是依据1943年出版的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所言:“《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2]这段言论实际上来自李贤等注《后汉书》。应当说,无论是李贤,还是郑玄,都没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
清代毛奇龄对“束修”多有研究。他的《四书剩言》说:“《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贽见薄物,其见于经传者甚众。如《檀弓》‘束修之问’,《穀梁传》‘束修之肉’,《后汉·第五伦传》‘束修之馈’,则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问之礼为言。若《孔丛子》云‘子思居贫,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为当也’,此犹是偶然馈遗之节。至《北史·儒林传》‘冯伟门徒束修,一毫不受’,则直指教学事矣。又《隋书·刘炫》‘博学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然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则直与《论语》‘未尝无诲’作相反语。又《唐六典》‘国子生初入学,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则分束帛与修为二,然亦是教学贽物。近儒以汉后史书多有‘束修’字作‘约束修饬’解,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荐管宁‘束修其躬’类,遂谓‘束修’不是物,历引诸‘束修’词以为辨。夫天下词字相同者多有,龙星不必是龙,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强同之,谬矣。试诵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将之而上乎?”[13]在毛奇龄看来,《论语》所谓“束修”,一直以来就被解读为“贽见薄物”,是见面的薄物之礼,同时,汉以后所修史书中所谓“束修”,有些并不是指薄物之礼,而是指“约束修饬”。显然,当时就“束修”是“贽见薄物”还是“约束修饬”,有过激烈争论,而毛奇龄赞同把《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中的“束修”解读为“贽见薄物”。
后来的方观旭撰《论语偶记》,根据李贤等注《后汉书》所引郑玄注“束修”而言“谓年十五以上”,说:“盖古人称‘束修’,有指束身修行言者。《列女传》秋胡妇云‘束发修身’,《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得宿卫’,《后汉·延笃传》曰‘且吾自束修以来’,马援、杜诗二传又并以束修为年十五,俱是郑注佐证。《书传》云‘十五入小学,殆行束修时矣。'”[14]这里把“束修”又解读为束身修行。
刘宝楠《论语正义》接受毛奇龄的说法,认为《论语》中的“束修”为“贽礼”,即见面礼。他还说:“李贤《后汉·延笃传》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注《论语》曰“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郑注,所以广异义。人年十六为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故举其所行之贽以表其年。”[15]也就是说,郑玄把“束修”说成是“年十五以上”,是指“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刘宝楠还认为,“《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曰‘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皆以‘束修’表年,与郑义同”,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束修”是“以约束修饰为义”。因此,刘宝楠说:“后之儒者,移以解《论语》此文,且举李贤‘束带修饰’之语,以为郑义亦然,是诬郑矣。”[16]他认为,郑玄不可能把《论语》“束修”解读为“束带修饰”。
与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于“束修”的解读不同,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是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郑君注如此,汉时相传之师说也”。黄式三还说:“《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笃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异于郑君。然《书·秦誓》孔疏引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为某传束修一介臣之证,是孔郑注同。盖年十五以上,束带修饰以就外傅,郑君与孔义可合也。”[17]显然,黄式三是要说明“束修”为“束带修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还是黄式三《论语后案》把“束修”解读为“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他们都把“束修”看作“礼”,并且与“十五岁以上”有关。但这并不可说明“束修”是就“十五岁以上”而言,不可由此得出“束修”就是指“十五岁以上”。
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根据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黄式三《论语后案》中的有关文献材料,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实际上是把重点落在年龄上,而不是落在“礼”上,这不仅不同于刘宝楠《论语正义》,而且也不同于黄式三《论语后案》,甚至不同于所有把“束修”看作“礼”的解读。把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更像是说孔子在做义务教育。
二、“修,脯也。十脡为束”
继孔安国注《论语》“自行束修以上”之后,皇侃之疏明确讲“束修,十束脯”,“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后来,孔颖达讲“束修,十脡脯也”,北宋邢昺也疏曰:“束修,礼之薄者。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而来学者,则吾未曾不诲焉,皆教诲之也……‘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者,按:《书传》言束修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18]此外,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在论及“束帛、束修之制”时说:“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疋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19]可见,在皇侃讲“束修,十束脯”之后,较多学者认为“束修”为十脡脯,其实只是一束。在数量上有了变化。
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曰:“修,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20显然,朱熹所作的注释,就“束修”而言,与皇侃有一定的相像性。如前所述,在皇侃那里,“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而在朱熹《论语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皇侃讲“束修,十束脯”,朱熹讲“修,脯也。十脡为束”,与孔颖达、邢昺等相同。朱熹还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21]这里所谓“羔雁是较直钱底”,即皇侃所说“中则卿羔、大夫雁”。
其实,朱熹不仅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束修”解读为“修,脯也。十脡为束”,而且还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也同孔颖达《礼记正义》那样讲“束修,十脡脯也”[22]。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在数量上等同于皇侃所谓“束修,十束脯”。
平心而论,朱熹对于《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解读,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过皇侃、孔颖达、邢昺。那么,朱熹的解读,其新意又何在?
以朱熹为首的宋代理学家,其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实际上并不只是停留于字面上,其重点更在于探讨这些字面含义背后的所以然之理,因此,要在弄清楚孔子所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字面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即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朱熹所谓:“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在朱熹看来,之所以要“自行束修以上”,是因为如果没有“束修”,那么就“不知来学”,“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与此相反,“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照朱熹这一解读,孔子之所以要求“自行束修以上”,其目的只是在于表明来学之诚意,并能够据此而有往教之礼;而之所以“未尝无诲”,是因为“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
在《论语》中,孔子讲“仁”,“仁者爱人”;而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则不仅讲“仁”,而且讲“仁者之心”“仁之体”。朱熹注《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23]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指自己欲立达,由此而想到他人也欲立达,这是“以己及人”,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至于仁者为什么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引程颢所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已。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24]也就是说,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朱熹注“束修”所说“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能够“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做到“诲人不倦”。
孔子不仅讲“仁”,而且讲“恕”;而朱熹则不仅讲“以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还讲“推己及人”,并讨论“仁”“恕”之别。朱熹注《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并引述程颢所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25]。认为孔子所谓“恕”,即“推己及人”。据《论语》所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对此,朱熹注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6朱熹认为“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为“仁”,而“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恕”;“仁”为“不待勉强”“自然而然”,“恕”为“推己及人”。
朱熹不仅讲“仁”“恕”之别,而且特别强调“推己及人”为“仁之方”。朱熹《论语集注》在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的同时,又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27]认为“能近取譬”,从自己所欲而推知他人所欲,推己及人,是仁之方。据《论语》所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朱熹注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28]认为孔子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及人”,可以终身行之。这也就是朱熹注《论语》“束修”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因而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也就是说,若能够“自行束修以上”,以礼而来,那么就能知得来学,因而才有“往教之礼”。
三、“束修”之理
孔子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如果把“束修”解读为“干肉”,很容易使今天的人们联想到孔子是把“束修”当作教人的报酬。问题是,孔子肯定不是为了获得“束修”而教人;在一定意义上看,“自行束修以上”只是“礼”,所以孔安国解读为“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汉唐儒家把“束修”解说为或干肉之类的“贽见薄物”,或“束带修饰”,都是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朱熹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29]在朱熹看来,“礼”和“钱”是不能混淆的,而有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才有“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由此亦可推想,李泽厚《论语今读》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并且能够得到一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担心如果把“束修”解读“干肉”,会与教人之报酬混为一谈,而导致所谓“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并与孔子讲“有教无类”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冲突。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束修”,包含了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认为“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但是,在朱熹看来,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不止于“礼”,又超出了“礼”的层面,而是在落实“推己及人”之恕道,也就是说,通过“自行束修以上”便能够知得来学者,而最重要的是知得来学者的诚意,由此才能有往教之礼。
朱熹对于孔子所谓“束修”的解读,重视谢良佐、杨时等人的说法。他的《论孟精义》引谢良佐所说:“束修不必用于见师,古人相见之礼皆然。言及我门者苟以是心至,未尝不教之。”又引杨时所说:“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30]也就说,“束修”不只是“礼”,而是“心”,是来学者的诚意之心。朱熹的理解与此完全一致。为此,朱熹还说:“诸说无他异。”[31]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之后,接着又注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指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32]朱熹还说:“愤悱,便是诚意到;不愤悱,便是诚不到。”[33]在朱熹看来,老师教学生,要根据学生是否有诚意而施教,这与朱熹注“束修”所表达的根据来学者是否有诚意而决定是否行往教之礼,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对于孔子所谓“束修”,既可以从“礼”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礼,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以表达为心意。
同时,由于“束修”的目的在于教学,“束修”之礼和“束修”之理对于教学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束修”之礼,作为“礼”,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外在的。教者为“束修”而教,学者为“束修”而学,“束修”与教学二分,不能真正落实儒家“为仁由己”的“为己之学”。与此不同,“束修”之理,作为“理”,即为心之诚意,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内在的。诚意不仅是教学的内在根本,也是为人之根本,所以,“束修”之理所包含的诚意,与教学互为一体。
因此,朱熹把孔子所谓“束修”解说为“修,脯也。十艇为束”,虽然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朱熹从“理”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理,诠释为“心”,超越了以往只是从“礼”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礼。而且,这种对于“束修”的形而上学的诠释,也是后来学者未能超越的。
四、余论
对于朱熹解读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提出的“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后来的王夫之多有批评。他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己之心而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而安能已于吾心哉!始来学者,执束修以见,则已有志于学,而愿受教于吾矣。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益教者之道固然,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学而上达,存乎其人而已矣。”[34]王夫之认为,教者在于教,而不能不教,这是教者之道,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心”。显然,这是针对朱熹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言。
诚然,就一般道理而言,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二者是一致的。就具体而言,对于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朱熹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王夫之讲“未尝无有以诲之”,二者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对于没有执束修以见,且不知是否来求学者,朱熹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无论是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还是没有执束修以见的非来学者,都必须是“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显然,王夫之对于儒学之道的理解,与朱熹是有一定差异的。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述了历史上各种关于“束修”的解读,也包括清代毛奇龄《四书剩言》、刘宝楠《论语正义》、黄式三《论语后案》的观点,但并没有就“束修”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只是引述《四书诠义》所言:“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而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公之至也。”[35]显然,这一引述大致依据朱熹的解读而来。所谓“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讲孔子无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这与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是一致的;所谓“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正是依据朱熹所言“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朱熹生活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宋代理学追求自我,追求成圣,自我意识日益强大,人们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朱熹重视人与人之间因气禀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尊重他人自己的选择,讲“不知来学,
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这与当时人们强调自我意识,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王夫之所在的明末清初,人们的自我意识日渐弱化,启蒙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夫之强调“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也可见得其合理之处。换言之,儒家在不同文化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体现出内部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儒学来说,其根本宗旨是不变的。先秦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当然,仅仅停留于这些基本原则是不够的。正是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朱熹既讲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又要求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在对孔子所谓“束修”的诠释中,既提出“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的基本原则,又阐发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具体待人之道。相对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朱熹不仅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且还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这不仅在对“束修”的诠释上超越了以往的诠释,而且对于理解儒家的待人之道也颇有新意,同时对于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尊重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相比之下,现代各种解读,大都不是接朱熹而来,也不同于王夫之,而显得较为肤浅。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依据汉唐诸儒的一家之言,把“束修”只是理解为“束修”之礼,不能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为“束修”之理,很容易被误解为孔子教人,需要收礼,需要获得报酬,而不是出于“仁”之理;李泽厚《论语今读》讲“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则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似乎能够克服孔子教人需要收礼、“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误解,体现一种平等的义务教育,但这样的解读,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文本依据。
一、束修:是“礼”还是“十五岁以上”
对于《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西汉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4]孔安国只是讲到“奉礼”而需要“束修”,并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进一步解读。孔安国还在注《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时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伎艺,其心休休焉。”[5]也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解读。
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但是其《论语郑氏注》大约于宋初开始失传。近年来,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研究有较大进展。有学者以《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塔那184号墓72TAM184:18/7(b),18/8(b)《论语郑氏注》之《述而》篇第9、10行为底本,并且结合敦煌文献,认为唐写本郑玄注的原文应该是:“自(始)行束修,谓年十五之时(奉?)酒脯。十五已上有恩好者以施遗焉。”[6]“束修”对应的是“酒脯”。郑玄还在讲到亲朋好友结婚、自己有事而无法前往需要遣人送礼时,说:“其礼盖壶酒、束修若犬也。”孔颖达疏曰:“礼物用壶酒及束修。束修,十脡脯也。若无脯,则壶酒及一犬。”[7]显然,在郑玄那里,“束修”是一种与“酒脯”有关的礼物。
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曰:“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应者也。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贽,至也,表已来至也。上则人君用玉,中则卿羔、大夫雁、士雉,下则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其中或束修、壶酒、一犬,悉不得无也。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贽,行束修以上来见谒者,则我未尝不教诲之。故江熙云:‘见其翘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贽见。修,脯也。孔注虽不云修是脯,而意亦不得离脯也。’”[8]显然,皇侃把“束修”解读为“十束脯”,并且还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与“脯”有关。该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孔颖达虽然在《礼记正义》中说“束修,十脡脯也”,但在《尚书正义》中疏孔安国“如有束修一介臣”时,却说:“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节,此亦当然。”[9]他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为“束带修节”。
南北朝范晔撰《后汉书》,唐代李贤等为之作注。其中注《伏湛传》“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曰:“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10]又注《延笃传》“且吾自束修以来”,曰:“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1]在这里,李贤既讲“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又讲“束修谓束带修饰”,应当是指年十五以上自行束修,“束带修饰”。因此,“束修”是就“束带修饰”而言,而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可见,汉唐时期诸儒解读“束修”,既有如郑玄解读为与“酒脯”有关的礼物,或皇侃解读为“脯”,也有如李贤解读为“束带修饰”,虽然郑玄、李贤的解读与“年十五以上”有关,但都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李泽厚《论语今读》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是依据1943年出版的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所言:“《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2]这段言论实际上来自李贤等注《后汉书》。应当说,无论是李贤,还是郑玄,都没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
清代毛奇龄对“束修”多有研究。他的《四书剩言》说:“《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贽见薄物,其见于经传者甚众。如《檀弓》‘束修之问’,《穀梁传》‘束修之肉’,《后汉·第五伦传》‘束修之馈’,则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问之礼为言。若《孔丛子》云‘子思居贫,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为当也’,此犹是偶然馈遗之节。至《北史·儒林传》‘冯伟门徒束修,一毫不受’,则直指教学事矣。又《隋书·刘炫》‘博学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然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则直与《论语》‘未尝无诲’作相反语。又《唐六典》‘国子生初入学,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则分束帛与修为二,然亦是教学贽物。近儒以汉后史书多有‘束修’字作‘约束修饬’解,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荐管宁‘束修其躬’类,遂谓‘束修’不是物,历引诸‘束修’词以为辨。夫天下词字相同者多有,龙星不必是龙,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强同之,谬矣。试诵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将之而上乎?”[13]在毛奇龄看来,《论语》所谓“束修”,一直以来就被解读为“贽见薄物”,是见面的薄物之礼,同时,汉以后所修史书中所谓“束修”,有些并不是指薄物之礼,而是指“约束修饬”。显然,当时就“束修”是“贽见薄物”还是“约束修饬”,有过激烈争论,而毛奇龄赞同把《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中的“束修”解读为“贽见薄物”。
后来的方观旭撰《论语偶记》,根据李贤等注《后汉书》所引郑玄注“束修”而言“谓年十五以上”,说:“盖古人称‘束修’,有指束身修行言者。《列女传》秋胡妇云‘束发修身’,《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得宿卫’,《后汉·延笃传》曰‘且吾自束修以来’,马援、杜诗二传又并以束修为年十五,俱是郑注佐证。《书传》云‘十五入小学,殆行束修时矣。'”[14]这里把“束修”又解读为束身修行。
刘宝楠《论语正义》接受毛奇龄的说法,认为《论语》中的“束修”为“贽礼”,即见面礼。他还说:“李贤《后汉·延笃传》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注《论语》曰“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郑注,所以广异义。人年十六为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故举其所行之贽以表其年。”[15]也就是说,郑玄把“束修”说成是“年十五以上”,是指“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刘宝楠还认为,“《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曰‘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皆以‘束修’表年,与郑义同”,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束修”是“以约束修饰为义”。因此,刘宝楠说:“后之儒者,移以解《论语》此文,且举李贤‘束带修饰’之语,以为郑义亦然,是诬郑矣。”[16]他认为,郑玄不可能把《论语》“束修”解读为“束带修饰”。
与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于“束修”的解读不同,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是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郑君注如此,汉时相传之师说也”。黄式三还说:“《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笃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异于郑君。然《书·秦誓》孔疏引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为某传束修一介臣之证,是孔郑注同。盖年十五以上,束带修饰以就外傅,郑君与孔义可合也。”[17]显然,黄式三是要说明“束修”为“束带修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还是黄式三《论语后案》把“束修”解读为“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他们都把“束修”看作“礼”,并且与“十五岁以上”有关。但这并不可说明“束修”是就“十五岁以上”而言,不可由此得出“束修”就是指“十五岁以上”。
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根据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黄式三《论语后案》中的有关文献材料,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实际上是把重点落在年龄上,而不是落在“礼”上,这不仅不同于刘宝楠《论语正义》,而且也不同于黄式三《论语后案》,甚至不同于所有把“束修”看作“礼”的解读。把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更像是说孔子在做义务教育。
二、“修,脯也。十脡为束”
继孔安国注《论语》“自行束修以上”之后,皇侃之疏明确讲“束修,十束脯”,“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后来,孔颖达讲“束修,十脡脯也”,北宋邢昺也疏曰:“束修,礼之薄者。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而来学者,则吾未曾不诲焉,皆教诲之也……‘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者,按:《书传》言束修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18]此外,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在论及“束帛、束修之制”时说:“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疋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19]可见,在皇侃讲“束修,十束脯”之后,较多学者认为“束修”为十脡脯,其实只是一束。在数量上有了变化。
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曰:“修,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20显然,朱熹所作的注释,就“束修”而言,与皇侃有一定的相像性。如前所述,在皇侃那里,“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而在朱熹《论语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皇侃讲“束修,十束脯”,朱熹讲“修,脯也。十脡为束”,与孔颖达、邢昺等相同。朱熹还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21]这里所谓“羔雁是较直钱底”,即皇侃所说“中则卿羔、大夫雁”。
其实,朱熹不仅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束修”解读为“修,脯也。十脡为束”,而且还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也同孔颖达《礼记正义》那样讲“束修,十脡脯也”[22]。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在数量上等同于皇侃所谓“束修,十束脯”。
平心而论,朱熹对于《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解读,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过皇侃、孔颖达、邢昺。那么,朱熹的解读,其新意又何在?
以朱熹为首的宋代理学家,其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实际上并不只是停留于字面上,其重点更在于探讨这些字面含义背后的所以然之理,因此,要在弄清楚孔子所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字面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即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朱熹所谓:“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在朱熹看来,之所以要“自行束修以上”,是因为如果没有“束修”,那么就“不知来学”,“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与此相反,“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照朱熹这一解读,孔子之所以要求“自行束修以上”,其目的只是在于表明来学之诚意,并能够据此而有往教之礼;而之所以“未尝无诲”,是因为“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
在《论语》中,孔子讲“仁”,“仁者爱人”;而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则不仅讲“仁”,而且讲“仁者之心”“仁之体”。朱熹注《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23]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指自己欲立达,由此而想到他人也欲立达,这是“以己及人”,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至于仁者为什么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引程颢所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已。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24]也就是说,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朱熹注“束修”所说“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能够“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做到“诲人不倦”。
孔子不仅讲“仁”,而且讲“恕”;而朱熹则不仅讲“以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还讲“推己及人”,并讨论“仁”“恕”之别。朱熹注《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并引述程颢所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25]。认为孔子所谓“恕”,即“推己及人”。据《论语》所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对此,朱熹注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6朱熹认为“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为“仁”,而“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恕”;“仁”为“不待勉强”“自然而然”,“恕”为“推己及人”。
朱熹不仅讲“仁”“恕”之别,而且特别强调“推己及人”为“仁之方”。朱熹《论语集注》在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的同时,又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27]认为“能近取譬”,从自己所欲而推知他人所欲,推己及人,是仁之方。据《论语》所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朱熹注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28]认为孔子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及人”,可以终身行之。这也就是朱熹注《论语》“束修”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因而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也就是说,若能够“自行束修以上”,以礼而来,那么就能知得来学,因而才有“往教之礼”。
三、“束修”之理
孔子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如果把“束修”解读为“干肉”,很容易使今天的人们联想到孔子是把“束修”当作教人的报酬。问题是,孔子肯定不是为了获得“束修”而教人;在一定意义上看,“自行束修以上”只是“礼”,所以孔安国解读为“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汉唐儒家把“束修”解说为或干肉之类的“贽见薄物”,或“束带修饰”,都是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朱熹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29]在朱熹看来,“礼”和“钱”是不能混淆的,而有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才有“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由此亦可推想,李泽厚《论语今读》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并且能够得到一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担心如果把“束修”解读“干肉”,会与教人之报酬混为一谈,而导致所谓“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并与孔子讲“有教无类”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冲突。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束修”,包含了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认为“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但是,在朱熹看来,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不止于“礼”,又超出了“礼”的层面,而是在落实“推己及人”之恕道,也就是说,通过“自行束修以上”便能够知得来学者,而最重要的是知得来学者的诚意,由此才能有往教之礼。
朱熹对于孔子所谓“束修”的解读,重视谢良佐、杨时等人的说法。他的《论孟精义》引谢良佐所说:“束修不必用于见师,古人相见之礼皆然。言及我门者苟以是心至,未尝不教之。”又引杨时所说:“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30]也就说,“束修”不只是“礼”,而是“心”,是来学者的诚意之心。朱熹的理解与此完全一致。为此,朱熹还说:“诸说无他异。”[31]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之后,接着又注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指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32]朱熹还说:“愤悱,便是诚意到;不愤悱,便是诚不到。”[33]在朱熹看来,老师教学生,要根据学生是否有诚意而施教,这与朱熹注“束修”所表达的根据来学者是否有诚意而决定是否行往教之礼,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对于孔子所谓“束修”,既可以从“礼”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礼,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以表达为心意。
同时,由于“束修”的目的在于教学,“束修”之礼和“束修”之理对于教学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束修”之礼,作为“礼”,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外在的。教者为“束修”而教,学者为“束修”而学,“束修”与教学二分,不能真正落实儒家“为仁由己”的“为己之学”。与此不同,“束修”之理,作为“理”,即为心之诚意,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内在的。诚意不仅是教学的内在根本,也是为人之根本,所以,“束修”之理所包含的诚意,与教学互为一体。
因此,朱熹把孔子所谓“束修”解说为“修,脯也。十艇为束”,虽然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朱熹从“理”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理,诠释为“心”,超越了以往只是从“礼”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礼。而且,这种对于“束修”的形而上学的诠释,也是后来学者未能超越的。
四、余论
对于朱熹解读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提出的“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后来的王夫之多有批评。他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己之心而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而安能已于吾心哉!始来学者,执束修以见,则已有志于学,而愿受教于吾矣。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益教者之道固然,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学而上达,存乎其人而已矣。”[34]王夫之认为,教者在于教,而不能不教,这是教者之道,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心”。显然,这是针对朱熹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言。
诚然,就一般道理而言,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二者是一致的。就具体而言,对于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朱熹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王夫之讲“未尝无有以诲之”,二者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对于没有执束修以见,且不知是否来求学者,朱熹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无论是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还是没有执束修以见的非来学者,都必须是“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显然,王夫之对于儒学之道的理解,与朱熹是有一定差异的。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述了历史上各种关于“束修”的解读,也包括清代毛奇龄《四书剩言》、刘宝楠《论语正义》、黄式三《论语后案》的观点,但并没有就“束修”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只是引述《四书诠义》所言:“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而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公之至也。”[35]显然,这一引述大致依据朱熹的解读而来。所谓“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讲孔子无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这与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是一致的;所谓“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正是依据朱熹所言“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朱熹生活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宋代理学追求自我,追求成圣,自我意识日益强大,人们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朱熹重视人与人之间因气禀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尊重他人自己的选择,讲“不知来学,
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这与当时人们强调自我意识,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王夫之所在的明末清初,人们的自我意识日渐弱化,启蒙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夫之强调“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也可见得其合理之处。换言之,儒家在不同文化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体现出内部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儒学来说,其根本宗旨是不变的。先秦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当然,仅仅停留于这些基本原则是不够的。正是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朱熹既讲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又要求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在对孔子所谓“束修”的诠释中,既提出“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的基本原则,又阐发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具体待人之道。相对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朱熹不仅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且还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这不仅在对“束修”的诠释上超越了以往的诠释,而且对于理解儒家的待人之道也颇有新意,同时对于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尊重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相比之下,现代各种解读,大都不是接朱熹而来,也不同于王夫之,而显得较为肤浅。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依据汉唐诸儒的一家之言,把“束修”只是理解为“束修”之礼,不能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为“束修”之理,很容易被误解为孔子教人,需要收礼,需要获得报酬,而不是出于“仁”之理;李泽厚《论语今读》讲“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则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似乎能够克服孔子教人需要收礼、“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误解,体现一种平等的义务教育,但这样的解读,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文本依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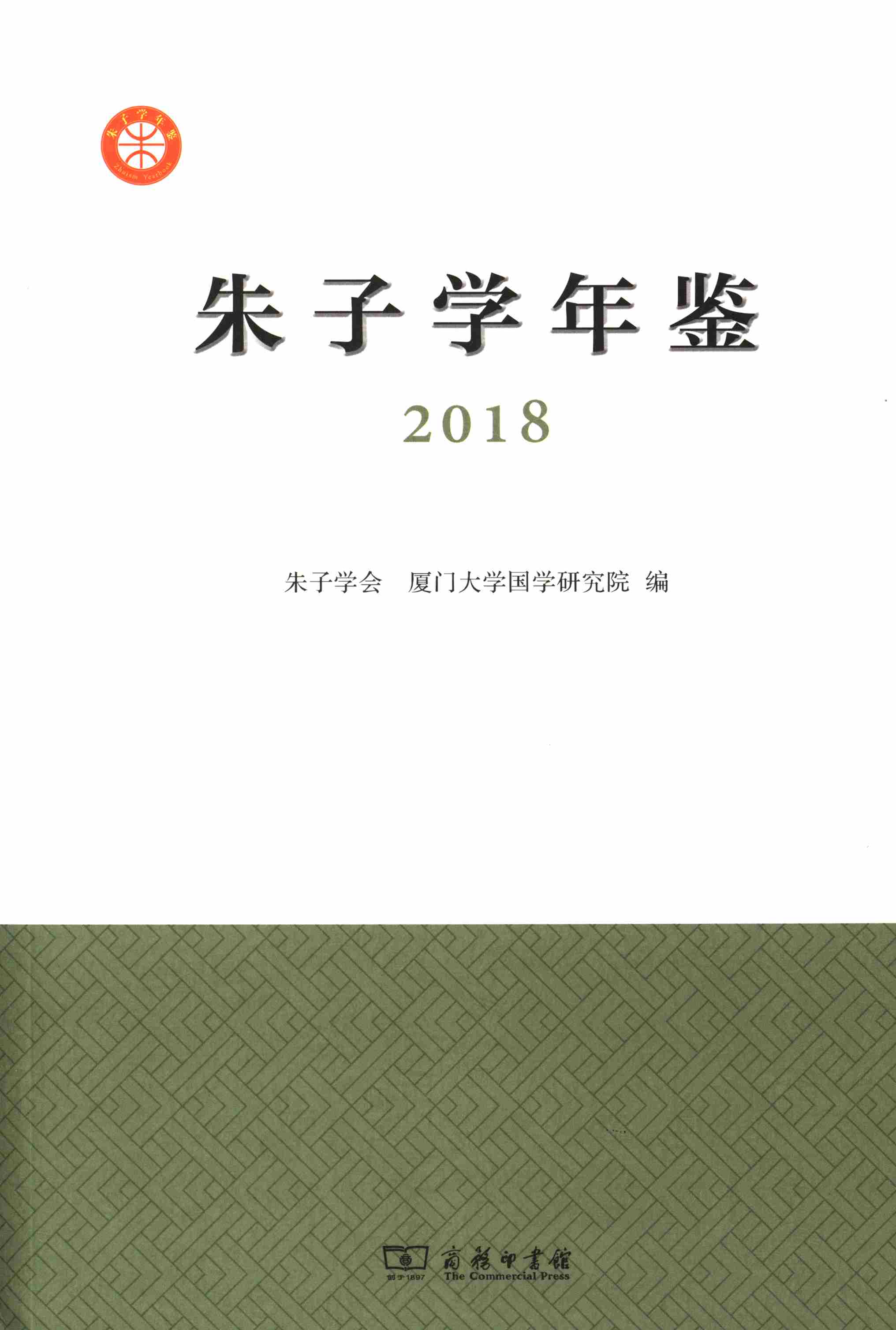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