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偏言”与“专言”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8)》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299 |
| 颗粒名称: | 仁的“偏言”与“专言” |
| 其他题名: | 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063-072 |
| 摘要: | 本篇文章讨论了程颐关于仁义礼智信四德和五常的关系。程颐认为,仁是四德之一,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发于外表现为恻隐之心;恕是入仁之门,但不同于仁本身;礼是定分,即确定权利和义务的准则;智是知也,即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信则是有此性者也,即具备诚信的品质。文章还介绍了程颐的“偏言”和“专言”说,以及如何将四德和五常联系起来。 |
| 关键词: | 程颐 仁义礼智信 讨论 |
内容
从“偏言”与“专言”的角度解说仁,起初是程颐仁说中一个比较专门的话题,即由他之解《周易》而来的“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1]。程颐之论“仁”,自然是其理论本身的需要,但其渊源,却始自先秦以来儒家对于“仁”这一概念的不同界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仁义礼智诸德关系的认识。鉴于“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理学家对此发生兴趣就是理所当然的。其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
一
《周易·乾卦·彖辞》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等语,这是程颐言仁之“偏言”与“专言”说的源头。在语词上,“乾元”之称,显系将卦名“乾”与卦辞“元亨利贞”之“元”整合起来的结果。《彖辞》称颂乾元伟大,突出的是乾的创始作用,天地万物均凭借乾元而生起。
唐代孔颖达引《子夏传》的始、通、和、正为元亨利贞“正义”,并将其概括为四德。所谓“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2]。德者,得也,乾卦凭借其阳性、阳气的创生作用,使所生的万物秉性和谐并得到了最符合它们自身需要的利益和效果。从而,性气合一的生生流行就是乾卦四德的实质,这也是天地间最大的善。圣人则当效法乾元生生而推行此善道。
不过,就《彖辞》自身而言,却既未言善也不及仁,立足善与仁解四德,是《文言》进行再加工的结果。后者曰: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四德之间,元之长善,实质在长人,而人者仁也,所以善之长便归结到君子的以仁为体和仁爱的普施;其余三德,亨通而合乎礼,必然会有众美之嘉会;物各得其利而不害,体现的乃是义之和谐;而固守正道,则足以成为事之主干。那么,天德一方的元亨利贞,已经演绎成为人世的人伦道德体系,四德由天道进入到了人道。参照孔颖达的疏解,四德又与春夏秋冬相配,体现的是一年四季生长收藏的气化运行。从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3]。人世间的德行均因法天而来。君子仁道充实又博爱众生,所以能成为人之尊长。就是说,“泛爱施生”的普遍关爱作为善或仁德,正是君子效法上天“元”德的结果。
在孔颖达看来,天道的四德流贯于人世实际就是仁义礼智,但《文言》本身只言及仁义礼而并未及智,这如何能与人世之四德相通呢?而且,如果不是死咬文字的话,孟子当年强调的仁义礼智之性已经可说是人世之四德,并有“四端”与之相呼应。所以孔颖达也需要予以衔接过渡。他的解释是“(元亨利贞)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智者,行此四事,并须资于知”[4]。就是说,就元亨利贞落实于政事言,表现为仁义礼信,智在这里不是缺失,而是所有这“四事”的施行,都不能离开智慧的运用。所以,智虽未言,却早已融入仁义礼信之中。
孔颖达之解,显然是以五常来回应四德。事实上,在儒家学者那里,五常与四德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各自对应的天道和解释的侧重有所不同,即相对于木火土金水五行,言仁义礼智信五常;相对于春夏秋冬四时,则言仁义礼智四德。所以,孔颖达能方便地将智加入其中,这就为后人直接以仁义礼智诠释四德做好了基本的铺垫。
二
程颐对元亨利贞四德的解释,自然要借鉴汉唐人士的智慧,因而注意四德与五常的关联。对于其间的关系,他的看法是:
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须要分别出。若仁则固一,一所以为仁。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一作便有)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若以东为西,以南为北,则是有不信。如东即东,西即西,则无(一有不字)信。[5]
程颐把四德五常都收归到性上去说。从性上言“五事”,必然会涉及仁的统一与五常之“分别”以及仁性与爱情等方面的关系,还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信”的问题。在这里,仁作为“一”,实际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仁本身就是四德或五常之一,作为内在之性,发于外便表现为恻隐之心;二是仁又是一个融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整体性概念,能够以一统四,正是仁所具有的品格。至于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意味凡事出以公心,人我一致而无偏爱。但恕道虽说是入仁之门,又毕竟不等于仁本身。问题到最后,其实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与表现于外的“四端”即恻隐等情感的关系问题。四端所以未涉及信,在于它不是必要,因为信是相对不信而言,也不存在信的情感或发端的问题。
程子又说: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礼者别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万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恻隐之类,皆情也,凡动者谓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后见,故四端不言信。)[6]
以“公”解仁,突出了爱人的公平无私和普遍性的品格;义礼智则在表明对对象的把握和处置恰到好处;信却有不同,它只是在确认五常之性的存在。可以说,凡物皆有性,性静而情动,恻隐等等便属于性之发动的情感。同时,性本于天而与人的生命同在,这直接就意味着信(性在人的成立),故不需另言。只有在天性被障蔽即“不信”的时候才会出现信的问题。那么,在程颐看来,五性之中是“仁义礼智”四德必有而“信”可缺,这既可以说是重视信——四德五常都必须是实存而不可少;但也表明,理学家的心性(性情)理论建构,可以不需要信的范畴而建立。当然,这并不会危及信作为五常之一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程颐虽也不少论及五常,但往往是作为过渡,重点已转向对仁之义及与其他诸德关系的考虑。他说: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乾健坤顺之类,亦不曾果然体认得。)[7]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说明程颐根本否定了汉唐诸儒对“仁”之义的解释。仁作为儒学的核心范畴,在程颐之前已有多方面的揭示,譬如恻隐、孝悌、博爱、公正,等等。但是,程颐以为它们都有不完全的缺憾。关键的问题,是要能从“仁之道”中分别出五常来。如果只是讲仁的“兼体”,仁就只能是与诸德相互平行的概念,而否定了其包容和统属的功能。在程颐看来,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如同人的头脑与四肢的关系一样,其主从位置是不应当混淆的。《文言》讲“元者善之长”,并不意味着“元”作为众善之首只是位序的优先,即与随后的亨利贞是并列的概念,而是强调仁具有统属四德的性质,它作为“善之长”而顺序演绎成四德,仁德生生而有全体。故通过八卦来揭示的《易》之大义,就是通过乾元来彰显的生生之仁。圣人则因其“体法于乾之仁”而能“长人”,而“体仁,体元也”[8]《文言》的体仁,归结到圣人(君长)效法于乾元而长人上。
从卦象上说,乾为天,但天又有“专言”与“分言”之别:“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9]就此来看,“天”之一词,如果分从形体、主宰、功用、妙用或性情的不同方面言,可以用天、帝、鬼神、神、乾的不同概念去表述;但若专就“天”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道。“专”之字,在程颐那里有专门、专一、专擅等内涵,“专言”即意味专门集中言,并带有整体而非部分的意义:“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10]与之对应的“分言”,自然是分别就“天”的一个方面特征而言之,这可以从生生流行与横向展开的不同角度去进行揭示。比方,“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11]四德之义的广大,由乾元的“善大”步步引出,“善之长”是仁德,也是贯通四德的最重要的性质。
因而,程颐又说:
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12]乾元的伟大,就在于其所贡献的创始万物之道。四德、五常的意义也都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程颐以五常之仁解说四德之元,立足点可以说是仁的生意。“偏言”就是“分言”,即只就每一德或每一常自身而论,着重在这“一事”自身的性质、表现及特征等等;“专言”在此则不仅有专门集中言之义,更是突出了包容统属的功能。因为不论四德的亨利贞还是五常的义礼智信,都来源于乾元或仁的生气流淌,它们作为不同的德目,各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特色,但终究又依赖并被包含在元或仁的善之统体之中。从而,天地万物、人伦五常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既有主从之分又相互发明、既有整体一贯又有各自特色而不能互相代替的结构。
程颐提出仁义礼智的“偏言”与“专言”说,中心都是围绕仁说话,因为仁事实上具有不同的性能,不可能以一个标准来限定。孟子当年讲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等“四心”而表现为人的不同道德情感及意志行为。这里虽然突出了四德的区分,但它们四者毕竟又构成一个同“根于心”的德性整体,故其区分与总成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孟子终究没有合性理与生理为一的仁的概念,仁主要作为德性、情感存在而非生生之源,所以四德虽是内在的却不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后来韩愈讲仁、义、道、德的顺序递进,仁义已随道德主体的践行而有逻辑地展开,相互间已具有一种有机的关联。[13]到程氏兄弟,随着对《易》之“生意”和“生之谓性”等命题的重新审视和吸纳,生意的流淌已成为他们仁学理论建构必不可少的内在黏合剂。比方程颢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4]
将韩愈的道德仁义代入,“生”所以能作为天地之大德,就在于它在根本上促成了仁之善德源源不绝地生长,并通过天地气运交感而凝聚成各自形体性命的过程,使普遍之善凝聚为个体之性(善)。在此人与天地“一物”的意义上,人之爱人,其实就是人物同一的普遍仁性付诸实现,而不应当自我局狭。人既有禀赋了此必然的生意,恻隐之心的生发就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程颐同样以“生道”定义仁心的发端,认为“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15]。而且,“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6]。恻隐之心的触发,正赖于由生意而来的仁性的发动;而一当仁性发动,乾元生,义礼智诸德遂会因时因地而生成。此一机制颇受朱熹推崇,他称赞道:“程子‘谷种’之喻甚善。若有这种种在这里,何患生理不存!”[17]随此生意而下,“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18]。当然,程颐本人并未有朱熹这样的明确论述,但从其乾元始万物的道理和“体仁,体元也”[19]的原则来说,因生意而有四德的有机整体,也是符合程颐思想的逻辑的。
三
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涵摄宇宙论的生理,重在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已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但是,作为话题的提出者,程颐自己对区分仁之“偏言”与“专言”毕竟没有做出更多的发明,而且本身也存在灵活解释的问题。他留给后来的学者及其仁说理论的,更主要的是一个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或标准。朱熹在与其弟子的交流中对此便多有讨论。例如:
(朱熹)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以气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仁则为慈爱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逊;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问:“如何不道‘鲜矣义礼智’,只道‘鲜矣仁’?”曰:“程先生《易传》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专言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义也在里面;‘知觉谓之仁’,便智也在里面。如‘孝弟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爱而言。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才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20]
春夏秋冬、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可以解释为天(乾元)之生物的过程。“坯朴里便有这底”,说明仁性内在,随其生发和流行于人世,表现为真实可信的四德五常及其慈爱、刚断、谦逊、明辨诸情感品行。但学生的问题也由此开始。即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不说“鲜于义礼智”,这当作何理解?朱熹于是以程颐论“专言”和“偏言”作为鉴别标准去规范孔门的论仁诸说,他为此举过不少例证,就此段论述而言,“孝弟为仁之本”“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等被划归偏言;而“仁者必有勇”“知觉谓之仁”“克己复礼为仁”等则成为专言。
具体来说,一方面,“孝弟为仁之本”“泛爱众而亲仁”之间尽管也有孝亲与泛爱众的差别,但总体都是围绕爱人发论,并不涉及仁与其他德行的关联,故朱熹归之于偏言;而学生发问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言下之意是“鲜矣”也应当包含义礼智在内——这实际上是将仁视作专言。朱熹对此没有直接回答,他在《集注》中曾引程子的“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说明,巧言令色“绝无”仁,或曰仁者绝不会巧言令色。[21]而在此处,由于只是针对“巧言令色”者绝非真心爱人这一事,尚未涉及刚断、谦逊、明辨等其余德行的问题,仁在此与义礼智之间便是并列而非包容的关系,故仍归于偏言。另一方面,智、仁、勇本为一体,《中庸》称“所以行之者一也”,即言一已含三,故归于专言;至于“克己复礼为仁”,由于在克己去私或曰“为公”的氛围下,内在之仁昭显,义礼智本来已融于这一工夫之中,四德贯通为一个整体,故当属于专言的范畴。
不过,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专言”问题,常常又是将其纳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2]的框架中去处理的,体现出他对这一问题更多的思考。如说:“‘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23]如此的分合,可以放在他的理一分殊格局来看,即凡有一物便有一物之理,理虽不可见,但从发于外的爱、宜、恭敬辞逊、分辨是非的行为,可推知它们各自都源于其内涵之理;而所有分殊之理又统一到仁这一总理即心之德中,此种仁包四德的心之德,就是朱熹的“保合太和”[24]。那么,如此的分合就不只是概念的辩解,在现实中,由于仁作为“生理”而发生作用,它实际表现为一体连续的过程。如:
先生曰:“某寻常与朋友说,仁为孝弟之本,义礼智亦然。义只是知事亲如此孝,事长如此弟,礼亦是有事亲事长之礼,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为心之德,则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专言则包四者’是也;‘爱之理’,如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动处便见。有感而动时,皆自仁中发出来。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圆池,池虽不同,皆由水而为之也。”[25]
孝悌是根基性的道德践履,但它之生成又依赖于内在的仁性,并表现为对父母兄弟的亲爱之情;相应地,义礼智分别体现在践行孝悌的适宜恰当、礼仪周全及对孝悌之道的认知把握上。就此分别地看待仁义礼智各自的特性和表现说,都可归于偏言;但是,四德又都依存于心并统一于孝悌的行为,再由孝悌(亲亲)推广到仁民、爱物,使仁的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就后者论,仁作为心之德,已将义礼智包容在内,随事有感而发。不论仁的发作流动怎样表现,如水流成池而有大小方圆,但总之都是同一水所造成,事实上是同一个仁,所以谓之专言。那么,偏言与专言在朱熹又是可以相互过渡的。
因此,偏言和专言,实际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譬如朱熹对“小仁”和“大仁”的分析:“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26“小仁”与“大仁”的比喻不是不可以,因为这有助于认识清楚各自的定位和内涵,但又不能以僵化的态度去截然对待。在根本上,仁只有一个,偏言与专言是从不同层面对仁之意蕴的阐发。所以,对于仁的“偏言”与“专言”问题,“看得界限分明”只是问题的一面,更要注意到双方的相互包容:“说着偏言底,专言底便在里面;说专言底,则偏言底便在里面。”27]如在孟子,说“仁,人心也”是谓专言之仁,因为义礼智本是仁心发散的产物;但同时孟子又言“仁之实,事亲是也”,是特指孝亲这一事,仁又成了偏言。所以“专言”与“偏言”都是“相关说”的。[28]
“相关说”者关联孔子论仁的不同解答,但还有一种情况,即同一句话既可以是偏言又能够做专言,例如前面提及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是归于偏言;但他又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如从心之德的视域去看[29],又可以归于专言。之所以如此,基本点仍在于生气流行,“心之德”便可以是“爱之理”也。朱熹解答说:
“‘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气上看。如春夏秋冬,须看他四时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凉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气之长,秋是生气之敛,冬是生气之藏。若春无生物之意,后面三时都无了。此仁所以包得义礼智也,明道所以言‘义礼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抚使,更无一个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抚也。今学者须是先自讲明得一个仁,若理会得后,在心术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见得此仁,则心术上言仁与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30]
“爱之理”与“心之德”的沟通,需要从一气流行又有四时界限上去看。一方面,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各有其性,凉寒热之性本身不能生物,只有温厚的春气,才是天地生物之心的最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春气温厚又不止于一时,它是流动不息的。在充满生物之意的春气熏陶下,夏秋冬的热凉寒之性被化解,热成为生气之长,凉成为生气之敛,寒则成为生气之藏,一切融入整体的生意之中。不论是观念上辨仁,还是实践中施仁,都能够贯通无碍。从此生意看问题,便能够领会程颢之言“义礼智皆仁也”的意义。朱熹举例是福建路安抚使通常由福州知州兼任,两个职位是同一个人任,对这同一人来说,州之专守与路之巡察,即偏言与专言是整合为一体的。
那么,从根本上说,只要生生不息,便仁德常在。“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31]一切都要归到天地生物之心上说,天地人物的情感发用,都是此心的作用和表现。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关键在能否亲切体验。所以一旦能祛除己私,人的居处、执事、事亲、事兄直至恕物的各种活动,都是仁体的流行。所谓“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2]。
因而,不论是仁的“偏言”与“专言”,还是“爱之理”与“心之德”,重点仍在仁的融会贯通。如果真正明白了“仁”之义,则双方的沟通便不是问题。按朱熹《仁说》的归纳: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33]
朱熹的仁说从《易传》走过来,强调“君子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34]。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元亨利贞,由于仁之生意的不可断绝,仁义礼智四德的一以贯之就是必然的。分别从体用关系说,在体一方,仁包仁义礼智而构成为整体的德性;在用一方,爱恭宜别之情统一于恻隐而无所不贯,相对于“偏言”的特定发明,朱熹可能更看重“专言”的一体流行。不过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熹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四德各自的体用,实际上都可统一到仁德自身的体用关系上。基于生气流行,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学者所以需要在“克己复礼为仁”上做功夫,就在于克尽己私才能使仁性昭显,私欲去而公(天)理显,普天下流行的是同一个温厚生意,无所适而不在。
一
《周易·乾卦·彖辞》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等语,这是程颐言仁之“偏言”与“专言”说的源头。在语词上,“乾元”之称,显系将卦名“乾”与卦辞“元亨利贞”之“元”整合起来的结果。《彖辞》称颂乾元伟大,突出的是乾的创始作用,天地万物均凭借乾元而生起。
唐代孔颖达引《子夏传》的始、通、和、正为元亨利贞“正义”,并将其概括为四德。所谓“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2]。德者,得也,乾卦凭借其阳性、阳气的创生作用,使所生的万物秉性和谐并得到了最符合它们自身需要的利益和效果。从而,性气合一的生生流行就是乾卦四德的实质,这也是天地间最大的善。圣人则当效法乾元生生而推行此善道。
不过,就《彖辞》自身而言,却既未言善也不及仁,立足善与仁解四德,是《文言》进行再加工的结果。后者曰: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四德之间,元之长善,实质在长人,而人者仁也,所以善之长便归结到君子的以仁为体和仁爱的普施;其余三德,亨通而合乎礼,必然会有众美之嘉会;物各得其利而不害,体现的乃是义之和谐;而固守正道,则足以成为事之主干。那么,天德一方的元亨利贞,已经演绎成为人世的人伦道德体系,四德由天道进入到了人道。参照孔颖达的疏解,四德又与春夏秋冬相配,体现的是一年四季生长收藏的气化运行。从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3]。人世间的德行均因法天而来。君子仁道充实又博爱众生,所以能成为人之尊长。就是说,“泛爱施生”的普遍关爱作为善或仁德,正是君子效法上天“元”德的结果。
在孔颖达看来,天道的四德流贯于人世实际就是仁义礼智,但《文言》本身只言及仁义礼而并未及智,这如何能与人世之四德相通呢?而且,如果不是死咬文字的话,孟子当年强调的仁义礼智之性已经可说是人世之四德,并有“四端”与之相呼应。所以孔颖达也需要予以衔接过渡。他的解释是“(元亨利贞)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智者,行此四事,并须资于知”[4]。就是说,就元亨利贞落实于政事言,表现为仁义礼信,智在这里不是缺失,而是所有这“四事”的施行,都不能离开智慧的运用。所以,智虽未言,却早已融入仁义礼信之中。
孔颖达之解,显然是以五常来回应四德。事实上,在儒家学者那里,五常与四德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各自对应的天道和解释的侧重有所不同,即相对于木火土金水五行,言仁义礼智信五常;相对于春夏秋冬四时,则言仁义礼智四德。所以,孔颖达能方便地将智加入其中,这就为后人直接以仁义礼智诠释四德做好了基本的铺垫。
二
程颐对元亨利贞四德的解释,自然要借鉴汉唐人士的智慧,因而注意四德与五常的关联。对于其间的关系,他的看法是:
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须要分别出。若仁则固一,一所以为仁。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一作便有)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若以东为西,以南为北,则是有不信。如东即东,西即西,则无(一有不字)信。[5]
程颐把四德五常都收归到性上去说。从性上言“五事”,必然会涉及仁的统一与五常之“分别”以及仁性与爱情等方面的关系,还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信”的问题。在这里,仁作为“一”,实际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仁本身就是四德或五常之一,作为内在之性,发于外便表现为恻隐之心;二是仁又是一个融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整体性概念,能够以一统四,正是仁所具有的品格。至于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意味凡事出以公心,人我一致而无偏爱。但恕道虽说是入仁之门,又毕竟不等于仁本身。问题到最后,其实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与表现于外的“四端”即恻隐等情感的关系问题。四端所以未涉及信,在于它不是必要,因为信是相对不信而言,也不存在信的情感或发端的问题。
程子又说: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礼者别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万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恻隐之类,皆情也,凡动者谓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后见,故四端不言信。)[6]
以“公”解仁,突出了爱人的公平无私和普遍性的品格;义礼智则在表明对对象的把握和处置恰到好处;信却有不同,它只是在确认五常之性的存在。可以说,凡物皆有性,性静而情动,恻隐等等便属于性之发动的情感。同时,性本于天而与人的生命同在,这直接就意味着信(性在人的成立),故不需另言。只有在天性被障蔽即“不信”的时候才会出现信的问题。那么,在程颐看来,五性之中是“仁义礼智”四德必有而“信”可缺,这既可以说是重视信——四德五常都必须是实存而不可少;但也表明,理学家的心性(性情)理论建构,可以不需要信的范畴而建立。当然,这并不会危及信作为五常之一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程颐虽也不少论及五常,但往往是作为过渡,重点已转向对仁之义及与其他诸德关系的考虑。他说: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乾健坤顺之类,亦不曾果然体认得。)[7]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说明程颐根本否定了汉唐诸儒对“仁”之义的解释。仁作为儒学的核心范畴,在程颐之前已有多方面的揭示,譬如恻隐、孝悌、博爱、公正,等等。但是,程颐以为它们都有不完全的缺憾。关键的问题,是要能从“仁之道”中分别出五常来。如果只是讲仁的“兼体”,仁就只能是与诸德相互平行的概念,而否定了其包容和统属的功能。在程颐看来,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如同人的头脑与四肢的关系一样,其主从位置是不应当混淆的。《文言》讲“元者善之长”,并不意味着“元”作为众善之首只是位序的优先,即与随后的亨利贞是并列的概念,而是强调仁具有统属四德的性质,它作为“善之长”而顺序演绎成四德,仁德生生而有全体。故通过八卦来揭示的《易》之大义,就是通过乾元来彰显的生生之仁。圣人则因其“体法于乾之仁”而能“长人”,而“体仁,体元也”[8]《文言》的体仁,归结到圣人(君长)效法于乾元而长人上。
从卦象上说,乾为天,但天又有“专言”与“分言”之别:“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9]就此来看,“天”之一词,如果分从形体、主宰、功用、妙用或性情的不同方面言,可以用天、帝、鬼神、神、乾的不同概念去表述;但若专就“天”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道。“专”之字,在程颐那里有专门、专一、专擅等内涵,“专言”即意味专门集中言,并带有整体而非部分的意义:“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10]与之对应的“分言”,自然是分别就“天”的一个方面特征而言之,这可以从生生流行与横向展开的不同角度去进行揭示。比方,“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11]四德之义的广大,由乾元的“善大”步步引出,“善之长”是仁德,也是贯通四德的最重要的性质。
因而,程颐又说:
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12]乾元的伟大,就在于其所贡献的创始万物之道。四德、五常的意义也都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程颐以五常之仁解说四德之元,立足点可以说是仁的生意。“偏言”就是“分言”,即只就每一德或每一常自身而论,着重在这“一事”自身的性质、表现及特征等等;“专言”在此则不仅有专门集中言之义,更是突出了包容统属的功能。因为不论四德的亨利贞还是五常的义礼智信,都来源于乾元或仁的生气流淌,它们作为不同的德目,各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特色,但终究又依赖并被包含在元或仁的善之统体之中。从而,天地万物、人伦五常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既有主从之分又相互发明、既有整体一贯又有各自特色而不能互相代替的结构。
程颐提出仁义礼智的“偏言”与“专言”说,中心都是围绕仁说话,因为仁事实上具有不同的性能,不可能以一个标准来限定。孟子当年讲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等“四心”而表现为人的不同道德情感及意志行为。这里虽然突出了四德的区分,但它们四者毕竟又构成一个同“根于心”的德性整体,故其区分与总成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孟子终究没有合性理与生理为一的仁的概念,仁主要作为德性、情感存在而非生生之源,所以四德虽是内在的却不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后来韩愈讲仁、义、道、德的顺序递进,仁义已随道德主体的践行而有逻辑地展开,相互间已具有一种有机的关联。[13]到程氏兄弟,随着对《易》之“生意”和“生之谓性”等命题的重新审视和吸纳,生意的流淌已成为他们仁学理论建构必不可少的内在黏合剂。比方程颢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4]
将韩愈的道德仁义代入,“生”所以能作为天地之大德,就在于它在根本上促成了仁之善德源源不绝地生长,并通过天地气运交感而凝聚成各自形体性命的过程,使普遍之善凝聚为个体之性(善)。在此人与天地“一物”的意义上,人之爱人,其实就是人物同一的普遍仁性付诸实现,而不应当自我局狭。人既有禀赋了此必然的生意,恻隐之心的生发就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程颐同样以“生道”定义仁心的发端,认为“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15]。而且,“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6]。恻隐之心的触发,正赖于由生意而来的仁性的发动;而一当仁性发动,乾元生,义礼智诸德遂会因时因地而生成。此一机制颇受朱熹推崇,他称赞道:“程子‘谷种’之喻甚善。若有这种种在这里,何患生理不存!”[17]随此生意而下,“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18]。当然,程颐本人并未有朱熹这样的明确论述,但从其乾元始万物的道理和“体仁,体元也”[19]的原则来说,因生意而有四德的有机整体,也是符合程颐思想的逻辑的。
三
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涵摄宇宙论的生理,重在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已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但是,作为话题的提出者,程颐自己对区分仁之“偏言”与“专言”毕竟没有做出更多的发明,而且本身也存在灵活解释的问题。他留给后来的学者及其仁说理论的,更主要的是一个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或标准。朱熹在与其弟子的交流中对此便多有讨论。例如:
(朱熹)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以气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仁则为慈爱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逊;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问:“如何不道‘鲜矣义礼智’,只道‘鲜矣仁’?”曰:“程先生《易传》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专言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义也在里面;‘知觉谓之仁’,便智也在里面。如‘孝弟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爱而言。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才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20]
春夏秋冬、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可以解释为天(乾元)之生物的过程。“坯朴里便有这底”,说明仁性内在,随其生发和流行于人世,表现为真实可信的四德五常及其慈爱、刚断、谦逊、明辨诸情感品行。但学生的问题也由此开始。即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不说“鲜于义礼智”,这当作何理解?朱熹于是以程颐论“专言”和“偏言”作为鉴别标准去规范孔门的论仁诸说,他为此举过不少例证,就此段论述而言,“孝弟为仁之本”“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等被划归偏言;而“仁者必有勇”“知觉谓之仁”“克己复礼为仁”等则成为专言。
具体来说,一方面,“孝弟为仁之本”“泛爱众而亲仁”之间尽管也有孝亲与泛爱众的差别,但总体都是围绕爱人发论,并不涉及仁与其他德行的关联,故朱熹归之于偏言;而学生发问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言下之意是“鲜矣”也应当包含义礼智在内——这实际上是将仁视作专言。朱熹对此没有直接回答,他在《集注》中曾引程子的“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说明,巧言令色“绝无”仁,或曰仁者绝不会巧言令色。[21]而在此处,由于只是针对“巧言令色”者绝非真心爱人这一事,尚未涉及刚断、谦逊、明辨等其余德行的问题,仁在此与义礼智之间便是并列而非包容的关系,故仍归于偏言。另一方面,智、仁、勇本为一体,《中庸》称“所以行之者一也”,即言一已含三,故归于专言;至于“克己复礼为仁”,由于在克己去私或曰“为公”的氛围下,内在之仁昭显,义礼智本来已融于这一工夫之中,四德贯通为一个整体,故当属于专言的范畴。
不过,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专言”问题,常常又是将其纳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2]的框架中去处理的,体现出他对这一问题更多的思考。如说:“‘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23]如此的分合,可以放在他的理一分殊格局来看,即凡有一物便有一物之理,理虽不可见,但从发于外的爱、宜、恭敬辞逊、分辨是非的行为,可推知它们各自都源于其内涵之理;而所有分殊之理又统一到仁这一总理即心之德中,此种仁包四德的心之德,就是朱熹的“保合太和”[24]。那么,如此的分合就不只是概念的辩解,在现实中,由于仁作为“生理”而发生作用,它实际表现为一体连续的过程。如:
先生曰:“某寻常与朋友说,仁为孝弟之本,义礼智亦然。义只是知事亲如此孝,事长如此弟,礼亦是有事亲事长之礼,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为心之德,则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专言则包四者’是也;‘爱之理’,如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动处便见。有感而动时,皆自仁中发出来。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圆池,池虽不同,皆由水而为之也。”[25]
孝悌是根基性的道德践履,但它之生成又依赖于内在的仁性,并表现为对父母兄弟的亲爱之情;相应地,义礼智分别体现在践行孝悌的适宜恰当、礼仪周全及对孝悌之道的认知把握上。就此分别地看待仁义礼智各自的特性和表现说,都可归于偏言;但是,四德又都依存于心并统一于孝悌的行为,再由孝悌(亲亲)推广到仁民、爱物,使仁的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就后者论,仁作为心之德,已将义礼智包容在内,随事有感而发。不论仁的发作流动怎样表现,如水流成池而有大小方圆,但总之都是同一水所造成,事实上是同一个仁,所以谓之专言。那么,偏言与专言在朱熹又是可以相互过渡的。
因此,偏言和专言,实际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譬如朱熹对“小仁”和“大仁”的分析:“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26“小仁”与“大仁”的比喻不是不可以,因为这有助于认识清楚各自的定位和内涵,但又不能以僵化的态度去截然对待。在根本上,仁只有一个,偏言与专言是从不同层面对仁之意蕴的阐发。所以,对于仁的“偏言”与“专言”问题,“看得界限分明”只是问题的一面,更要注意到双方的相互包容:“说着偏言底,专言底便在里面;说专言底,则偏言底便在里面。”27]如在孟子,说“仁,人心也”是谓专言之仁,因为义礼智本是仁心发散的产物;但同时孟子又言“仁之实,事亲是也”,是特指孝亲这一事,仁又成了偏言。所以“专言”与“偏言”都是“相关说”的。[28]
“相关说”者关联孔子论仁的不同解答,但还有一种情况,即同一句话既可以是偏言又能够做专言,例如前面提及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是归于偏言;但他又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如从心之德的视域去看[29],又可以归于专言。之所以如此,基本点仍在于生气流行,“心之德”便可以是“爱之理”也。朱熹解答说:
“‘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气上看。如春夏秋冬,须看他四时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凉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气之长,秋是生气之敛,冬是生气之藏。若春无生物之意,后面三时都无了。此仁所以包得义礼智也,明道所以言‘义礼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抚使,更无一个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抚也。今学者须是先自讲明得一个仁,若理会得后,在心术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见得此仁,则心术上言仁与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30]
“爱之理”与“心之德”的沟通,需要从一气流行又有四时界限上去看。一方面,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各有其性,凉寒热之性本身不能生物,只有温厚的春气,才是天地生物之心的最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春气温厚又不止于一时,它是流动不息的。在充满生物之意的春气熏陶下,夏秋冬的热凉寒之性被化解,热成为生气之长,凉成为生气之敛,寒则成为生气之藏,一切融入整体的生意之中。不论是观念上辨仁,还是实践中施仁,都能够贯通无碍。从此生意看问题,便能够领会程颢之言“义礼智皆仁也”的意义。朱熹举例是福建路安抚使通常由福州知州兼任,两个职位是同一个人任,对这同一人来说,州之专守与路之巡察,即偏言与专言是整合为一体的。
那么,从根本上说,只要生生不息,便仁德常在。“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31]一切都要归到天地生物之心上说,天地人物的情感发用,都是此心的作用和表现。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关键在能否亲切体验。所以一旦能祛除己私,人的居处、执事、事亲、事兄直至恕物的各种活动,都是仁体的流行。所谓“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2]。
因而,不论是仁的“偏言”与“专言”,还是“爱之理”与“心之德”,重点仍在仁的融会贯通。如果真正明白了“仁”之义,则双方的沟通便不是问题。按朱熹《仁说》的归纳: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33]
朱熹的仁说从《易传》走过来,强调“君子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34]。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元亨利贞,由于仁之生意的不可断绝,仁义礼智四德的一以贯之就是必然的。分别从体用关系说,在体一方,仁包仁义礼智而构成为整体的德性;在用一方,爱恭宜别之情统一于恻隐而无所不贯,相对于“偏言”的特定发明,朱熹可能更看重“专言”的一体流行。不过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熹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四德各自的体用,实际上都可统一到仁德自身的体用关系上。基于生气流行,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学者所以需要在“克己复礼为仁”上做功夫,就在于克尽己私才能使仁性昭显,私欲去而公(天)理显,普天下流行的是同一个温厚生意,无所适而不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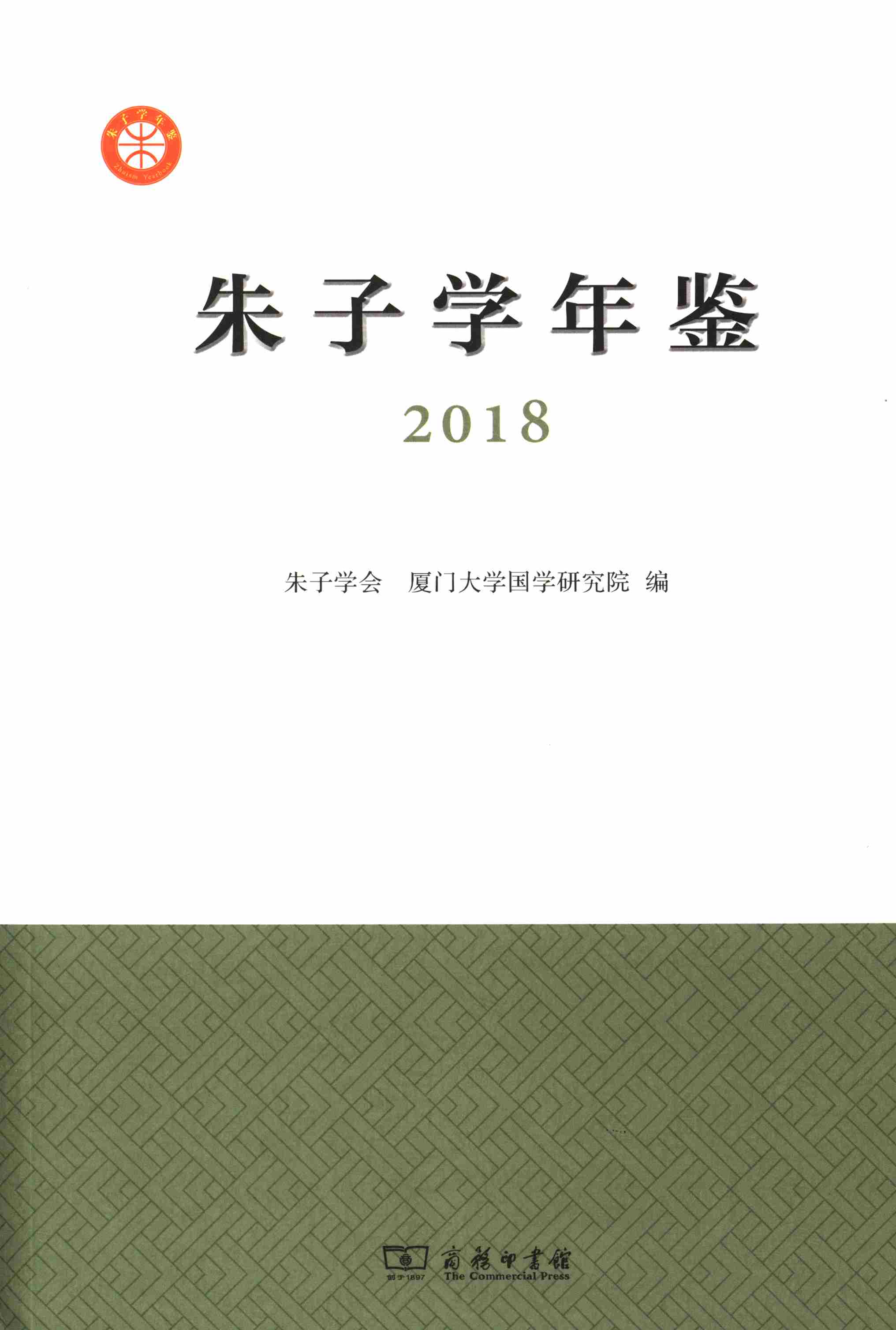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