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8)》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290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94 |
| 页码: | 027-12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南平市的朱子学年鉴2018年的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包括二程与朱子的道统说、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朱子的思想蓝图与当代中国思想的构建、仁的“偏言”与“专言”、朱熹对《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诠释及其意义、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朱熹审美观探究、性是理抑或理气合的内容介绍。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 视野 |
内容
二程与朱子的道统说
朱杰人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既热烈又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两位域外学者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位是德国学者苏费翔,一位是美国学者蔡涵墨。
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2010年,他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1]一文。这篇论文的一大突出贡献是,首次揭示了“道统”一词的词源性发展。他指出,早在唐代,“道统”一词即已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2]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朱子是第一个使用“道统”一词的历史公论[3]。此文梳理了朱子以前的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情况,指出,李若水、刘才邵、李流谦都使用过道统一词,他们的时间都早于朱子。苏氏还进一步指出,朱子使用“道统”一词也许和张浚、张栻父子有关。苏氏认为,在“道统”这一名词与概念的传衍、发展过程中,“朱熹的功劳就是把道统说普遍化,对后世影响甚大;自有朱熹才有人使用‘道统’这一简要的口号来推动相关的论述。在朱熹之前,虽然有学者用‘道统’来称呼学术或政治传承之体系,但是这都是偶然的、罕见的现象,并不能说朱熹以前已存在着一个有系统的‘道统论坛’”[4]。2015年,苏氏再次著文论《宋人道统论》。苏氏认为“‘道统’概念在宋代极其重要,又有强烈影响直到今日”[5]。此文的一个重要展开,是讨论了“道统”与“学统”“治统”的关系。他认为,“道统”概念的原始内涵是指儒家师系的传授系统,但它又与“学统”“治统”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大作《历史的严妆》是一本做翻案文章的著作。他所要推翻的历史是秦桧的反面形象。他发明了所谓“文本考古学”的新方法(恕我直言,所谓“文本考古学”,不外乎考据学与校勘学的所有方法与范畴),对我们的史学观与价值观做了颠覆性的解构,他的基本观点我无法苟同。但是他发现了一篇秦桧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所写的碑记。碑记中秦桧使用了“道统”一词:
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6]
蔡氏指出,这篇碑文申明“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7]。必须承认,蔡氏的发现是重要的,他的观察力也是洞彻的。这篇文献的发现,为宋代道统说的发生、发展以及对朱子道统论深层文化、政治背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依据。
二
“道统”一词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学说的传递。
《孟子·尽心下》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8]
一般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清晰地勾画出儒家道统传续的路线图。朱子在此篇之终有两段很长的注文。第一段注先引:“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9]引文完毕,朱子说:
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
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10]
朱子的按语,首先是对林氏对道统下传的悲观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传道的方式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之别,儒家道统的传续“期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就是说,儒家的道统,并不依靠人对人的口耳相传。“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11]朱子认为儒家的道统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不必担心它会失传。他预言“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其次,他又指出,《孟子》一书以孟子的这一段话终篇,一在表明孟子的儒道之传自有其统绪,二在强调此统之传正有待后来者承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不得辞者”这句话。这是说,孟子是个承担历史使命的人,他无法推辞他的责任。仔细玩味,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道统之传做铺垫。
韩愈是又一个对儒家道统传承做出明确界定的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2]苏费翔指出:“韩愈的系统,有当‘君’的圣王,又有当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没有圣王与贤臣互补关系(皋陶、伊尹等贤臣)。这样很明显分为治统(周公以前)与学统(孔子以后)两个阶段。”[13]
正如苏氏所指出的,无论是孟子的系统,还是韩愈的系统,乃至唐宋人有关道统传授系统的描述,都有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紧张:有位与无位。[14]如苏氏所言,在孔子之前,治统与学统是统一的,但是孔子之后,治统(有位之君臣)与学统(无位之圣贤)是分离的。这样的紧张,必然会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以宋代而言,君臣争夺道统承续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李若水,字清卿,北宋徽宗时人。他认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道统的继承人:“艺祖以勇智之资,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15]
李心传《道命录》卷二《范致明论伊川先生入山著书乞觉察》:“臣闻私议害国,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说诬民。处士横议,亦圣人之所不容。谨按通直郎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劝讲经筵……有轻视人主之意;议法太学……以变乱神考成宪为事。”[16]所谓“轻视人主”“议法太学”“变乱神考成宪为事”,即指妄图取代人主道统之尊的举动。
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是秦桧的碑记。记曰:
臣闻:王者位天地之中,做人民之主,故《说文》谓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为说也。杨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王者之道与儒同宗。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自周东迁,王者之迹熄。独孔圣以儒道设教洙泗之间,其高弟曰七十二子。虽入室升堂,所造有浅深,要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
共成一王之业,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纵之圣,系炎正之统;推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烬。
而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前未遭宋魋之难,讵肯易言之。
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方日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
绍兴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益国公臣秦桧谨记。[17]
蔡涵墨在分析这一碑记时指出:“这些引文又打造了基本的历史模拟脉络:上天保护逆境中的孔子,使孔子传承文王的政治、文化遗产给后世诸圣;如今上天再度在外祸与内乱之下护持宋高宗,使高宗得以再建‘道统’。”“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18]
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道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也注意到“道统”问题的特殊作用。他认为,北宋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这背后则是“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19]他认为,道学家建立“道统”说,是为了用“道”来范围“势”(位)。这“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积极方面则是引‘势’入‘道’。后一方面更是宋代理学家所共同寻求的长程目标”[20]。
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朱子的《中庸章句序》可以发现,朱子在历数道统传承的统绪中特别强调孔子以前都是“圣圣相承”,而“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21]。这是一句惊世骇俗的宣言,他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了尧舜之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序中把孔子之后的传承者一律归于“无位”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22]很显然,朱子是在刻意地把“道”与“势”做切割。如果说,在北宋,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是在觉醒的话,那么,到了朱子(南宋)应该是已经成熟了。
三
在朱子的道统谱系中,二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庸章句序》曰: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23]
这段论述,给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1.孟子以后,程氏兄弟是接续道统的人;
2.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
3.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
4.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们试着来分析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朱子认为程氏兄弟是道统的接续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朱子不是第一人。在朱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这一观点:
刘立之:“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孑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24]按,刘立之,“字宗礼,河间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与二先生有旧,宗礼早孤,数岁即养于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称其登门最早,精于吏事云。”[25]刘氏既为程颢最早的学生,则此说当在明道生前或死后不久。
朱光庭:“自孟轲以来,千有余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著,其闻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26]按,“公讳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师人……嘉祐二年登进士第……绍圣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初,受学于安定先生……后又从程伯淳、正叔二先生于洛阳。”[27]朱氏之论,当在程颢去世不久。但是,朱氏在程氏生前即已持此论,详见后引。
范祖禹:“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28]按,范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为给谏讲读官”[29]。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荐程颐,左正言朱光庭曰:“先生乃天民先觉,圣世真儒。”“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传。”[30]这说明,在二程兄弟生前,即已有传孔孟圣道之名声。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如游酢、吕大临、胡安国等。可见,这种说法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而将二程兄弟明确定义为孔孟之道接续者的,是程颐本人。程颢去世后,文彦博为其墓题碑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程颐为之作墓碑序曰: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国太师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慭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总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世而长存。勒石墓旁,以诏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31]
程颐的碑序十分重要,它既借文彦博之口明确了程颢是明孔孟之道之人,又借梳理道统传续之统,确立了程颢是道统当之无愧的继任者。在《明道先生行状》中他又说:“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32]这是说,程颢具有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
二程为道统的主要承续者,因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而成为定论,被学术界、思想界广泛接受。将二程定为道统的承续者,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道学(理学)在儒家道统传续的整个谱系中的正宗与主导的地位。从此,关于道统传承的各种纷争归于一统,道学在整个儒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道学家也取得了关于道统乃至整个儒学系统中的话语权。
为了构建以二程为宗主的道统谱系,朱子还编著了另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束景南认为:“朱熹的学派道统的正式确立是以《伊洛渊源录》一书为标志的。”[33]《伊洛渊源录》一书,构思于乾道九年(1173),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34]信中明言“周、程以来诸君子”,可见是为了谱叙传道之统。同年,朱子又为好友石墪《中庸集解》作序。序曰:
《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35]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朱子道统思想的建构此时已基本完成,并欲公之于众。但是《伊洛渊源录》一书却受到吕祖谦等人的非议。[36]朱子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37]于是朱子弃《伊洛渊源录》而以《中庸集解序》和《中庸章句序》为言,正式揭示出他的道统理论及谱系。
第二个问题: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这个问题包含着两层内涵。其一,朱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纠缠于文字训诂而不及义理:“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38]这样的学风,自然无法领悟到先圣思想的真谛。其二,“道在目前,初无隐蔽,而众人沉溺胶扰,不自知觉,是以圣人因其所见道体之实,发之言语文字之间,以开悟天下与来世。其言丁宁反复,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岂有故为不尽之言以愚学者之耳目,必俟其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哉?”[39]这就是说,道统的传递,固然离不开“言语文字”,但,言语文字并非靠“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诚如上文所说,朱子在这里强调了儒学道统的超越性和永恒的价值,这就为二程乃至他自己接续道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个问题: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在构建自己的道统理论时,朱子特别警惕佛老对儒学的影响。在建构怎样的道统谱系的问题上,他非常鲜明而坚决地把一切受佛老影响的儒者排斥在外。朱子的道统理论,其实包含着捍卫儒家学说纯正性的战斗精神。
第四个问题: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朱子认为程氏兄弟在道统传续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那么整个道统体系就要崩塌。所以他说“微程夫子”,就不可能得儒学、儒道之心。
四
苏费翔在《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中说:“他的目标似乎就是弘扬自己传道之说。”[40]在《宋人道统论》中,他又指出:“朱熹与孟子、韩愈大有不同,绝不认为今世道统失传,倡导宋初道统复兴之说,谓二程兄弟接续孟子之传,没有说二程之后再失传。可见朱熹很确定他自己是继承人。”[41]其实,在苏氏之前,已有很多学者指出,朱子似欲以道统传承者自居。[42]
朱子是否以道统的接续者自居?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朱子从不自诩为道统的继承人,但他一直不讳言,要以承续道统而自任。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43]
可见,朱子从小就立定了为先圣代言立言的志向。
在《中庸集解序》中,他说:
熹之友会稽石君墪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为一书,以便观览,名曰《中庸集解》……熹惟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言之详矣。熹之浅陋,盖有行思坐诵,没世穷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辞于其间!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熹诚不敏,私窃惧焉,故因子重之书,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则为有以真得其传。[44]
《中庸章句序》则曰: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耳。[45]
二序所言,均很自信和肯定地告示,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与注释是得到了先圣的真谛,他的目的就是要传道——使后之学者“或有取焉”。
在《大学章句序》中,他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46]在这篇序中,他明白无误地宣告,《大学章句》中有他自己的思想(正如土田健次郎所言“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张己说”)。但是这篇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熹“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他更明言:“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为务。然其所以言之者,则异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47]我们联系朱子在《孟子》全书结尾处的两段注文,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无疑是宣告了自己就是二程夫子的继任者。于是,道统的谱系最后一环就扣上了,也就是说,有宋一代的道统谱系最后完成了。
但是,自二程到朱子,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为什么继承二程道统的不是别人呢?朱子指出:“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二夫子于此既皆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记平居问答之辞。”[48]这是说二程的道统学说因没有著作留存,而仅靠他们弟子的著述得以流传。但遗憾的是,他的弟子们“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491。所以朱子非常感叹地说:“呜呼,是岂古昔圣贤相传之本意,与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50]更使朱子不安的是,程子的门徒们,依然受到佛老的污染而“不能无失”:“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51]于是,捍卫孔门道统的纯正,就成为朱子当仁不让的使命。
绍熙五年(1194),朱子65岁,辞官归乡,建沧州精舍,作《沧州精舍告先圣文》:
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维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援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载钻载仰,虽未有闻。赖天之灵,幸无失坠。逮兹退老,同好鼎来。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传之方来,永永无斁。[52]
此文为朱子晚年所作,可说是朱子关于“道统”说的一个总结性文献。在这篇并不很长的告文中,朱子再一次清晰地勾画了儒家道统的传续谱系,并自述了在传承道统的事业中自己的认识与作为。他自认为对先圣的道统精神已做到了“探原推本,敢昧厥初”,从此以后,道统之传将“传之方来,永永无斁”。这篇告文,充分显示出一个儒者的历史担当与强烈的使命意识。
朱子的道统说,最后的总结是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完成的。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二十一年,黄榦作《勉斋集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黄榦明确提出:“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文章结尾处,他又强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53]。至此,道统的谱系得以明确而清晰地表述,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遂成为定谳,并为学界所接受。
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
朱汉民
孔子及早期儒家通过整理“六经”,为“六经”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伏羲、神农、尧、舜、禹、文、武、周公的道统脉络,奠定了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同样,朱熹及宋儒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分别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论语集注》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脉络,完成了宋儒的道统论思想体系。在《四书集注》诸篇序说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希望继承孔子整理、诠释“六经”而确立儒家道统的思想传统。他主要是通过结集、诠释“四书”而建构理学,同时推动儒家道统论思想的成型。
朱熹延续北宋儒家从人物谱系、思想内涵方面探讨道统传承,尤其是能够从经典文本方面全面确立道统论。“四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经典体系,是因为它们被纳入数千年圣圣相传的儒家经典体系的道统脉络之中。朱熹通过确立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四书”学,同时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纳入数千年圣圣相传的儒家文明传道的脉络之中,实现对儒家道统论的重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就是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重建新儒家的道统论。
一、道统论与“四书”经典体系
考察儒学历史,道统思想总是与载道的经典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要真正实现道统论的重建,就必须把新的道统论与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结合起来。从中唐韩愈重提道统论,到宋初儒家学者倡导不同的道统谱系,道统问题成为宋初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从中唐到宋初,他们的道统谱系没有与相应的经典体系结合起来,其道统论就显得没有学术根基。
朱熹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统一起来。朱熹一生用力最多的是“四书”学研究。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1朱熹一生如此用功于“四书”,确实是因为他认为“五经”记载的先圣道统是由“四书”传承下来的,而他以及理学家群体通过注解“四书”就是传承孔孟道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将道统论与新经典体系即他集注的“四书”联系起来。
儒学文献分为经典、诸子与传记的不同类型,在儒学史上,“经”“传”“子”的区分既是十分明确的,但又是可以转换的。为了推动儒学发展和思想更新,一些由儒家的“子学”著作,可以转变为“六经”的“传”与“记”,“传”与“记”又可能转变为独立“经典”。儒家“经”“传”“子”的文献转换,往往根据的是儒学学术史、思想史演变的需求。为了推动儒学史的发展,汉儒确立和尊崇“五经”体系,同时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子学著作先后提升为传记著作;同样为了儒学史的发展,朱熹将汉代作为传记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提升为独立经典。但是,这不仅仅是文献形式的变换,中间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变化:前轴心文明的先王政典的地位在下降,而轴心时期儒家诸子的著作与思想,越来越居于儒家文献与儒家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
《中庸》《大学》作为先秦儒家的子学著作,已经在汉代编入《礼记》,尽管以后《礼记》也逐渐由传记之学演变为《礼》经,但唐以前《中庸》《大学》均不是独立经典,其思想的内涵、意义与“四书”学区别很大。宋儒开始了重建经典的行动,是由于儒家道统授受脉络,必须通过“载道之文”的经典体系才能够确立;反过来说,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子学著作提升为独立经典,需要一个儒家道统脉络的依据。于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四书”,开始由儒家子学和“五经”传记,逐渐演变、发展为独立经典,并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四书”学经典体系。
朱熹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确立为经典体系,必须确立这四部书是如何承接三代先王之道的。朱熹在“四书”的序说中,说明每一部书在传承三代先王之道的道统论意义。
孔子是儒学的创建者,他是“六经”的整理者,也是先王之道的自觉传承者,他的道统地位是儒家的基本共识。《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讲学的记录,是关于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所以,我们在《论语集注》书前的《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可以看到,朱熹并没有对《论语》这一部书做更多道统论的说明,而主要将道统的代表经典,放到其他三部著作的阐述上。朱熹在《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主要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论述、二程对《论语》的看法,进一步说明《论语》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朱熹在《读论语孟子法》引述程子的说法:“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21这是二程、朱熹的一个重要主张,即《论语》《孟子》是儒家经典之本,这与汉儒以“六经”为儒家经典之本、《论语》只是所谓“小经”有很大区别。他们特别强调了《论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代替“六经”,这就更加强化了《论语》的道统论意义。另外,在《语孟精义序》中,朱熹即称是书“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3],也是进一步说明《论语》一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性。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做了不一般的处理和论证。《大学章句序》,对《大学》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地位,做了特别的强调。一方面,朱熹强调治、教合一在道统史上的意义,他肯定从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先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君师”一体、“教治”合一,这体现出“继天立极”的道脉传承,儒家学说就是继承了上古圣王“教治”合一的传统,朱熹强调“《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4],就是强调《大学》是记载三代“教治”合一的传道之文。另一方面,朱熹强调《大学》一书是孔子传道曾子的重要典籍,他说:“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休,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51朱熹引用程子的说法,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6],故而他将《大学》分成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叙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7]。所以,朱熹从上述两个方面,充分肯定这一部“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的书,既保留了远古以来“君师”一体、“教治”合一的圣王之道,又是体现孔子、曾子二人传道精神的重要文献。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同样做了不一般的论证。在儒家典籍中,一直就有尧、舜、禹在传位的同时也传道的记载。《论语·尧曰》有尧帝语于舜帝之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也载有“允执其中”。以中道作为儒家道统授受的思想核心,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庸》这一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朱熹通过《中庸章句序》以系统阐述儒家道统思想。一方面,朱熹强调“中道”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肯定道统史上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即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8];另一方面,则是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在“不得其位”的情况下承接了中庸之道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而有贤于尧、舜”。孔子是“继往圣、开来学”的重要道统人物,再经过颜子、曾子之传,道统传到了子思,“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9]。由此可见,《中庸》一书在道统史上十分重要,它是代表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又是体现孔子、颜子、曾子、子思传承道统的文本。而且,《中庸》一书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是“子思引夫子之言”[10],其余各章则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11]。因此,朱熹也是从两个方面,肯定《中庸》一书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12]的书,是记载孔子、子思传道的重要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重要地位。
《孟子》原来是子学著作,但是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儒家学者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道统谱系上的重要文献,继而上升为经典。像《论语序说》一样,朱熹在《孟子序说》中,也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对孟子的评价,以及韩愈对《孟子》的看法,说明《孟子》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譬如,朱熹引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所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3]。朱熹还引韩愈的评价:“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14]在《孟子序说》中,朱熹摘录韩愈有关儒家道统传授谱系的论述,突出了《孟子》的道统意义。《孟子》终篇《尽心下》末章载有孟子的一段感慨,历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间隔均为五百余年,他们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但是却不断有后圣继起,他显然是关注孔子之后能否有继之者的重要现实问题。朱熹《孟子集注》即从道统论的立场出发做了解说,他说:“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15]
朱熹因孟子而发的“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的感慨,显然是对孟子千年之后的道统,是否有继之者的现实问题的追问。而他本人之所以会以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的诠释与建构,就是传承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来的道统。事实上,朱熹对孔子以来的士人传道经典重视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三代先王传道经典。
二、“四书”学与道统人物谱系
本来,所谓的“道统”就是指传道的人物统绪。但是,在关于道统的人物统绪问题上,儒家向来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既包括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也包括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与儒家“六经”有关。儒家道统谱系依据“六经”中两部不同的经典:一部是《尚书》系统的依据,作为“人君辞诰之典”[16],《尚书》文献的作者从尧、舜、禹开始到夏、商、周的先王,代表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人物谱系;另一部是《周易》系统的依据,《易传》有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经文上下篇,而孔子则作传文以解经,故而早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这两套系统既有相同点,又有重要的差别。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更是存在很大差别,一则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中哪些能够列入道统谱系?二则是儒学创建以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的不同朝代,儒学学术思潮不同,儒家学者旨趣各异,究竟谁才是儒学道统的代表,向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唐宋时期儒家士大夫面临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问题,故而他们特别需要强调、建构一个合乎时代需要的道统论。唐代韩愈的《原道》是道统论的重要文献,这一篇文章的观点十分明确:道统上溯至尧舜,下传至孟子。但是,韩愈在另外的文章中又肯定荀子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不仅仅是韩愈,唐代有许多儒家学者,包括长孙无忌、魏徵、杨惊、卢照邻、裴度等均认同“周孔荀孟”的道统人物谱系。[17]到了北宋初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道统谱系仍然十分多元化,他们对三代先王的道统谱系有互不相同的看法,尤其是对孔子以后能够列入道统人物谱系的儒家学者有大相径庭的见解。譬如,宋初理学先驱孙复、石介提出的道统说,就是在尧之前加上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六位圣王,在孟子之后加进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四位道统传人。而苏轼则提出了由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道统谱系。他提出孔孟之后,“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18]。其实,道统人物谱系的观念,反映了那个时代及其儒家学者的儒学思想状况。宋初道统人物谱系的多元化,体现出这一时期儒学复兴要求的强烈和新儒学思想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随着宋学的不断发展,宋学不同学派争鸣的同时道学思想体系成型,道学派的道统论逐渐成熟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程颢逝世之后,程颐作《墓表》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9]这样,程颐就以程颢直承孔孟,作为圣人之道在宋代的继承者,正式确立了道学派的道统论。在程门弟子的推动下,特别是南宋朱熹、张栻的倡导下,一种新的道统论确立并成为思想主流。
如前所述,程朱学派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确立统一起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中每一本书的作者做了介绍和论述。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推介,因他的序言是为了确立一套新经典体系,而确立新经典体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这些书的作者纳入上古时期的道统谱系。“六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是由三代圣王的道统人物而“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诸序中,对每一位作者做出说明时,势必会将他与道的授受脉络联系起来。“道统”这个词在朱熹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但是,真正赋予这个概念完整的道统论意义,特别是将道统的授受谱系与经典系统结合起来,还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在《中庸章句序》中使用了“道统”,并且从几个不同方面对其做了详细论证,因此朱熹被学界看作是宋学道统论的真正完成者。
我们进一步考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序言,看他如何建立起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为了强化这一道统人物谱系,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道统授受谱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统人物是“君师”合一的上古圣王,他们创造了“教治”合一的道统。朱熹提出:“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20]既是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同时也是为了强调儒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朱熹显然吸收了《易传》的思想,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尧、舜之前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追溯《中庸》的思想渊源,对儒家道统的先王传授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自上古以来道统便圣圣相传,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21]。在《尚书·洪范》《论语》中,均记载有尧、舜、禹授受“允执厥中”的事实,故而朱熹主要以《尚书》为依据,列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朱熹在《孟子说序》中,也特别引证了韩愈《原道》的观点,即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学说。
第二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及其诸弟子的道统授受谱系,他们均是无“君师之位”却能够兴道统之教,故而是重要的道统人物。朱熹在《论语序说》中引述司马迁的看法,肯定孔子在道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朱熹还在《论语集注》的终篇《尧曰》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孔子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他引述杨时的言论说:“《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22]显然,朱熹在这里引述杨时之言,就是以道统论解说孔子及其《论语》“明圣学之所传者”,即应该从道统的角度“著明二十篇之大旨”。《大学》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这不利于道统谱系的确立。朱熹以《大学》包括孔子的经一章,曾子作传十章,进一步确立《大学》的道统谱系。朱熹肯定曾子是《大学》的作者,主要是从道统论建构方面考虑的。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义,他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23朱子在道统人物谱系上,特别强调孟子的重要地位,在《孟子集注序说》中,朱熹引《史记·孟子列传》介绍孟子生平,重点阐释孟子的道统地位。他说:“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4然后,朱熹又通过引用韩愈、二程、杨时,进一步对孟子道统地位做出充分肯定。可见,在朱熹心目中他们所继承的儒家之道,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上承先王之道。
最关键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宋学人物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讨论的重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将宋代道学学派列入孔孟之道的道统脉络中来,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25]在同样讲义理之学的宋学学派中,程朱道学派特别重视《大学》,他们通过诠释《大学》而建构道学,就具有重要的道统谱系意义。另外,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也特别强调,程朱道学派在传授《中庸》学的道统意义。所以,《中庸章句序》和《大学章句序》一样,均凸显了程朱道学在道统谱系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选的注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集中了汉宋诸儒的注释,但是,朱熹最为重视的是程门诸子的思想。在《语孟集义序》中,朱熹曾经阐明《语孟精义》的原则,就是将二程之说“搜辑条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若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26]。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更是将程门道学之说作为其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其引述特别集中。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四书章句集注》共引用了32个学者的语录,其中居前的为二程及其弟子,占引用总数的一半以上。朱熹“四书”学以二程一派为依归的特点,恰恰体现出朱熹的“四书”学其实就是确立了程朱理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朱熹所述的道统论来看,道统授受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圣王、春秋战国的孔孟、宋代的程朱。这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诸序中论述道统人物谱系的特点。但是,如果从性质上看,朱熹所述的道统论只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即有“君师之位”的圣王道统与无“君师之位”的士人道统,这两种道统虽然有联系,但是其中的区别要特别关注。朱熹及其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心经典,就是突出了士人群体承担道统的重要意义。
三、“四书”学与道统核心思想
“道统”不仅要有传道的经典文献、人物谱系,而且特别关键的是要有“道”的核心思想。唐中叶韩愈在面临佛教、道教的盛行而作《原道》时,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义”。到了宋代,无论是面对儒学外部的不同思想信仰,还是儒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这是努力重建新儒学的士大夫必须解答的问题。
程朱确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就是认同“四书”体系里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体系中每一本书的基本宗旨与核心思想做了论述。早期儒家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共同思想特点,就是在继承三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提升和理论建构,其思想成果体现为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
三代先王留给儒家学者的文化遗产就是礼乐文明,这包括一整套宗教化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思想观念,早期儒家继承和改造了这一套礼仪规范,并且对这一套礼仪规范做出理性化的思想诠释和价值提升,创造出了“以礼归仁”“以礼制中”“以礼为教”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义、中庸、教化为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所谓“以礼归仁”,就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仁”的内在情感情操,以“仁”的道德情操、道德理想去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所谓“以礼制中”,也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中”的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以“中”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和治理方法。所谓“以礼为教”,就是通过道德教化,将“礼”的强制规范制度化解为个体道德自觉与社会优良风俗,以“教”的道德自觉与优良风俗完成“礼”的规范秩序和国家治理。
所以,宋儒所确立的“四书”学,其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他们选择、结集、诠释“四书”的目的,就是传承、弘扬、发展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四书”的每一本书既有对某一价值理念的特别关注与论述,又有对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的整体追求。
《论语》准确而全面地记载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对三代礼乐的先王之道的深刻思考,推动了“礼—仁”“礼—中”“礼—教”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这些核心思想也就是道统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仁道、中庸、教化均有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以,孔子是早期儒家仁、中、教的价值体系的奠基人。但是,如何深化、展开儒家仁、中、教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孔门诸弟子各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思想创造。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特别重视《大学》《中庸》《孟子》,恰恰在于这些早期儒家文献对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中、教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孟子》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仁义。从唐中叶韩愈的《原道》开始,就将孟子推举为孔子道统的继承者,后世始有“孔孟之道”的说法。而且,韩愈《原道》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们传承的道统内容就是“仁义”。宋儒继承了这一观点,朱熹在《孟子说序》中引证了韩愈《原道》以“仁义”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的观点。同时,朱熹又引证程子的观点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27]由此可见,从韩愈到二程、朱熹,均认可一个相通的观点,就是孔子与孟子传递的道统内容就是“仁”和“仁义”。但是,宋儒也发展了这一观点,韩愈仅仅是肯定孔孟之道的内容是仁义,而程朱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不仅包括性善、恻隐等心性论,还包括养气、存心等修身工夫论,这恰恰是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拓展,也是宋儒需要进一步诠释和发展的思想。孟子拓展了孔子的仁学,孟子以人的道德情感为经验基础,通过性善、恻隐等心性论思想,从人的内在的、情感的方面确立了儒家关于仁的核心价值;孟子又以义理之天为超验依据,将仁义与超越性的天道结合起来。另外,孟子还关注君子仁人如何自我修养,故而提出养气、存心等实践仁义的修身工夫论。程朱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就是希望以孟子的仁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仁学的不同思想维度。朱熹在《孟子说序》中重点引证道学宗师二程、杨时对《孟子》一书的见解,因为朱熹就是继承了二程、杨时关于《孟子》一书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仁学的理论化、实践化的拓展。
《中庸》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中庸”。《中庸》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这样一部原本是普通诸子学文献的书,如何能够在唐宋以来上升为核心经典?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这一本书集中讨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即中道;其二,这一本书对中道做了多维度的探讨,有利于中庸之道的哲学提升。可见,《中庸》潜在的思想文化价值决定了后来的地位提升。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是他关于道统论的最重要的文献,也是研究宋儒道统论必引的论著。这一篇文章通篇论述道统问题,将“中”认定为上古以来圣圣相传的道统内容,从而确立了中道在儒家道统授受过程中的特别价值。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说:“盖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28]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乃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亦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统的精神核心。“中”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近的思想来源,“中”是西周“礼”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一个是远的思想渊源,“中”是全面涉及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思维方式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而儒家思想,恰恰是既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也继承了华夏中道思想文化的传统。所以,儒家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追溯到三代时期,就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想象,而是有着久远文化渊源。在儒家的“六经”及诸子、传记中,“中道”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朱熹为弘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道”思想,将其作为儒家道统的内容。特别是提升了《中庸》的核心价值,将儒家中道与心性、天理统一起来。
《大学》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教”。《大学》也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它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核心经典的原因在于它强调了“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崇教传统,彰显了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教”。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强调《大学》之教其实就是体现了三代时期“教治”合一的思想传统,这也是儒家推崇的道统。但是,这一种将德性教化与政治治理合一的思想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体现。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首先就提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29]这一个“教人之法”的《大学》之教,源于“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道统。从上古的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道统脉络的人物,其实均是“继天立极”的“君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虽然无“君师”之位,但是继承先王道统而推行“先王之法”,故而有《大学》经一章留下来。然后通过曾子之传,而将此先王之道传递下来。《大学》只是古代先王的“教人之法”,其教人的内容其实就是《论语》《孟子》《中庸》的相关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所以,《论语》《孟子》《中庸》倡导的价值理念其实均可以纳入《大学》的大框架之中。《大学》是朱熹列入“四书”之首的经典,其理由他曾多次强调:“是以是书(指《大学》)之规模虽大,然其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30]《大学》所以被列为“四书”之首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也是为教)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为“教人之法”“教人之术”“修己治人之方”。至于《论语》《中庸》《孟子》等经典所列的教化论,均可分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朱熹明确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31]《大学》作为儒家为学纲目,将“修己治人之方”统统纳入其中。
朱子的思想蓝图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
李景林 王宇丰
引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一个时代总是有一种思想的生产,而思想的生产构成了一个时代学术的核心。所谓的“生产”,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是继承,我们过去常常说“批判继承”,而传统上讲的思想生产并非如此,主要侧重于文化生命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则是产生一种适合当代的思想,以此为基础而构建出一套适合当下所处时代的学术,这样的学术才能契合当下社会和一般的民众生活。
不过,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了中国当代思想的核心地位,学术则只具有一种客观研究和反映过去历史知识的地位。可以说,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当学术和思想产生分离后,学术就变成一种所谓的客观研究和反映过去的历史知识,就可能沦为列文森所形容的“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的命运。[1]
近些年来,大家逐渐意识到思想生产的重要性,有学者也逐渐地开始注重思想的创造。但是总体来说,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的生产,确实还未真正建立起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形态,而且也还没有为思想的产生做好充足的准备。具体来看,我们在问题意识、核心话题、思想论域、经典系统、致思路径、话语风格以及价值认同诸方面,尚未达成基本共识,未能明晰地找到方向上的共通性。
在中国哲学史上,朱子是一个特别有思想原创力的思想家,是宋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朱子以其广大完备之格局,建构并完成了思想生产的基本途径,为宋代儒学设计了宏阔的思想蓝图。我们可以从朱子有关宋代思想建构的蓝图设计,来对当代中国思想建构所可能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这一方面,做一些讨论。
一、朱子的思想蓝图
汉唐以降,儒学略偏重于社会政治层面、心性修养和精神皈依方面,乃渐次为佛家和道教所操持。一直到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兴起已过百年,孝宗的《原道辨》还在用“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来讲三教之功用,这说明佛教、道教的影响深刻而巨大,儒家只能被挤到“治世”一边,而个人身心修养和精神信仰方面还多为佛老思想所占据胜场。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
儒家如果没有一个精神信仰和形上层面的价值系统来作为其“外王”事业的基础,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即宋儒所面临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形上学的价值系统,这是宋儒的志向所在。宋儒自称其学为“实学”,认为当时熙宁变法的失败,从学术根源上讲,即由王安石之学“祖虚无而害实用”,把圣学的“外王”事业错置于释老的“性命之理”之上所致。[2]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宋儒的“心性义理之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应对释老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的冲击,以接续儒学固有的人文传统,为其“外王”之事业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形上学基础(体)。
朱子作为宋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此时代问题有着深刻的反思,并提出自己的一套应对的方法和路径,其所设想的思想蓝图,亦非常宏伟,可以说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子总结宋代的思想学术,设计了一套道路,或者在反思里构建生产思想的路径,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道统的建构
朱子建立圣道传承和思想学术的谱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代的圣道思想学术传承谱系,简称道统;二是宋代以来的思想学术传承谱系,简称道学之传。前者意在寻根,为儒家思想找到人文精神的历史根源;后者意在建立新统,为思想生产做准备。
道统的观念,起源甚早,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就已经萌生。《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已粗略勾勒出尧、舜、禹三代所传之道。《孟子·尽心下》则又有如下详尽的表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可以看作对这一圣道传承观念的一种表述。《论语·里仁》记载孔子有“闻道”之说,而在这里,孟子有关“闻而知之”和“见而知之”两种“知道”方式的区分,源自孔门后学,表现了一种圣道传承的观念,可以看作后儒道统观念之滥觞。[3]另外,我们从简帛《五行》“闻而知之者圣”与“见而知之者智”两命题,参照《礼记·乐记》的相关论述,可知先秦儒家认为文化、文明创制演进过程有“作”与“述”这两面之人格担当者。这一圣道传承论,特别强调“闻而知之者”对于圣道传承之贯通天人的原创性作用。
汉唐以来,一方面是儒家固有的“性命之学”的湮灭,另一方面是佛老的盛行,士人学者都到佛老思想那里去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据。李翱概括当时思想状况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4]由是,韩愈《原道》提出了他的道统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
按照韩愈的理解,儒家的“道”有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子、孟轲一贯下来的传承系统,称作“道统”。他认为,在孟子以后,这个性命之道就失传了。韩愈的这一道统说,大体为宋儒所接受,并继续弘扬。到了朱子那里,则明确而系统地阐述出来,《中庸章句序》云: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6]
朱子历述尧、舜、禹、汤、文、武(君),皋陶、伊、傅、周、召(臣),直到孔子、颜、曾相传之道统,又言道统传至孟子而后失其传。此所传道统之内容,朱子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十六字心传”。总而言之,这一“道统”说,其意义在于接续儒家的人文传统,为宋代的思想建构奠定文化生命之认同基础。朱子则自觉地接续这一具有历史根源性的历史人文传统。
另外,朱子还致力于对北宋以来思想(新统)之谱系的建构。在朱子的思想蓝图里,并不是赖其一人之力建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而是特别注重以往学术积累的积极成果,把这些思想资源凝聚成一种问题意识、核心话题、思想论域,并形成新的思想系统。这一点非常典型地反映在朱子和吕祖谦所编的《近思录》里。该书采摭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子书,是一部记述理学思想的著作,被认为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书。我们从这部书的分篇结构,就可以看出宋儒对学术思想内容的理解,这里面也表现了朱子重建宋代学统的努力。《近思录》共十四卷,原无篇名,《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记载了朱子对《近思录》各篇的逐篇纲目的说法:
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7]
显然,这完全是一个“内圣外王”的结构,与《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学说规模一致。清儒张伯行摘录朱熹书成《续近思录》,亦完全仿照《近思录》的体例。其书十四卷篇目如次:
第一卷道体、第二卷论学、第三卷致知、第四卷存养、第五卷克治、第六卷家道、第七卷出处、第八卷治体、第九卷治法、第十卷政事、第十一卷教学、第十二卷戒警、第十三卷辨别异端、第十四卷总论圣贤。[8]
这表现了时人对朱子学内涵的理解。这个学问规模,与先秦儒家是一致的。
如果说自尧、舜、禹、汤以至孟子的道统建构,意在文化认同和传统的接续,那么,对北宋以来的思想谱系之建构,则意在建立有宋一代以来学术思想的“新统”。前者注重在思想文化上的连续性、根源性,后者则注重在当代思想上的生产。这是朱子为宋代思想所勾画的整体画面和进入路径的第一个方面。
(二)经典系统的重构
每个时代的义理不同,面对的问题亦不同,经典系统的内容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经典还是原来那些历史上留存的文献典籍,但哪些是核心的、哪些是外围的,则会发生某些系统上的变化。宋儒思想的建构,首先表现为一种经典系统的重建。其所重经典,则由汉唐儒的“五经”,转向以“四书”为中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
在经典方面,朱子谓读经要循序渐进,应先“四书”后“六经”;“四书”次序,则宜先《大学》,次《论》《孟》,最后《中庸》。在朱子看来,《大学》三纲八目,概括了儒家由心性内圣功夫外显于治平外王事业的一个总的纲领,故为学须从作为圣学入德之门的《大学》开始;《论语》《孟子》应机接物,因时因事而发微言,循此以进,可以收具体而微、融会贯通之效;最后是《中庸》一书,荟萃儒家天人性命学说之精要。循《大学》《论》《孟》,而后会其极于《中庸》,便可建立学问思想的大本大经。由此再进于经史,乃能知其大义,而不致泥于文字训诂。朱子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9]朱子认为,经史包括丰富浩繁的古代制度、礼制方面的内容,这些东西属于一些历史知识,而“四书”才是儒家义理的精要。在朱子看来,“四书”“道理粲然”,易晓易解,但他同时也指出圣贤之言难精,须从精处用力,再读其他书则易为力,难者既精,粗者便易晓,因为后面的功夫里面已立大体,就不易流于偏颇。
从“四书”的系统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从思想义理上,则凸显了心性之学和道德修养的方面。汉唐的时候主要是以“周孔”并称,“周孔”表征意义在政治领域。到了宋代以后则强调“孔孟”,“孔孟”注重在心性修养或人文教化方面。像《孟子》和《中庸》,就涉及非常多的心性之学。第二,从道统意识上,则注重孔、曾、思、孟的传统。周公以前皆为圣王,乃政治上的传承,孔子之后则为学统的建立。
由此可见,一个经典系统的建立,不是随便选择几本书就可以想当然地确立出来。孔子以“六经”教授弟子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以《周易》《春秋》为中心,《周易》凸显了形上学,《春秋》凸显了要正名分,把这两个方面贯穿在“六经”里,则成为一个经典的系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现如今以传授知识为教学目的的教材编写,经典系统更是思想义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思想精神根底蕴含其中,义理脉络次第分明。
(三)心性义理之学的诠释
宋儒的道学或理学,就是传圣道之学;而此“道”的内容,即是一心性义理之学。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10]这即是以心性义理之学来概括宋儒之学。
汉唐以来,佛老在精神修养方面发展出一整套精微的思想学说,对儒学形成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宋儒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即是以经典系统为理论支撑,来自觉建构儒家自身的心性义理之学。宋儒多有出入佛老的为学经历,故能清醒地认识其心性论上吸引人们目光的地方,并加以批评,从而转化其为儒家的思想性质。朱子曾说:“佛家一向撤去许多事,只理会自身己;其教虽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会。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这下自无人。”[11]朱子在这里主要借佛家理会自我身心之教来批评一些儒者只是“守经”而不从切己处理会的弊病,佛家摒弃人伦而自修,这是与儒家的根本分歧,但是从某一侧面也引出了儒家自身的“为己之学”,自有一套就自家身心上理会的本领。借此形成儒家心性义理之学的自觉意识,逐渐使佛老一直占据着的心性修养领域重新回归到儒家经典系统的话语中来。
总之,宋儒所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绝非空言推论的产物。其所讨论问题,大率亦皆出自经典。诠释原则和思想重心的转变引发了与之相对应的经典系统的重构,通过经典的讲论、经典的诠释重新构建了一套核心范畴。由这些核心范畴建构起来的义理系统,和汉唐有很大不同,比如汉儒讲天人感应、三统三正、更化,但宋儒讲太极、理气、理欲、性命、心性、性情、性气、格致、本体功夫等,这些观念或范畴的凸显,围绕着心性修养和个体人格的养成这一核心话题,构成新的义理系统和新的理论视域,这就是思想的生产。在这种思想生产与经典之缘生互动的动态机制中,经典乃在不同时代获得其意义重构,参与思想的创造进程,成为思想生产的源头活水和生命源泉。
(四)对民间学术的关注
宋儒讲心性义理不是空谈心性,他们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这个“实学”不是后来所讲的事功之学,其所言“实学”:一者言学贵在自得;二者言学不离人伦日用。这便涉及宋代思想学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和落实问题。这个落实,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民间学术的讲论;二是社会生活样式的重建,也就是礼仪系统的重新建构。宋儒特别注重民间的教化,他们要把这一套东西落实到民间,同时也落实到心性,主要是心性的修养和人格的养成,其所重并不专在政治儒学。
宋代的书院非常发达,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说:“宋学形成之近因,则在书院之设立……宋代书院之设,遍于中国,造端实在南唐升元间,而大盛于宋庆历之际焉。”[12]当时书院非常多,有公立,有私立。其著名者,如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四书院。讲学著名者也很多,有齐同文、孙复、胡瑗、石介等。其实宋代的儒者,无论高居庙堂还是置身江湖,大多都在民间、在书院讲学,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胡瑗为北宋第一大教育家,讲授“明体达用”之学,所从学者达数千人之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学者,对当时的学风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宋史·儒林传》所载,当时礼部每年选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其弟子居朝和教授于四方者甚多。仁宗庆历年间,朝廷于京师立太学,下诏州县皆立学,并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教法。这对当时学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实每一个当时的儒者虽在官,既要治理一方,也要教化一方,担当着教化的职责。朱子当然也是这样的,他对民间的学术和讲学非常重视,经常在民间讲学,其在知南康军期间(孝宗淳熙年间),曾兴复白鹿洞书院,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院规,名曰《白鹿洞书院揭示》。《揭示》有五条:
一曰“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二曰“为学之序”: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三曰“修身之要”: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曰“处事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曰“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在院规后面,朱子讲了所制定院规的主要精神,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13]也就是说圣贤之学是非功利的。
中国传统学术传承,有官、私两条线。民间学术的传承,始终是社会教化的基础。当时的讲学,包括官方、民间的教学,官方的讲学也有民间性质,所谓的官方学说和民间学说是合而为一的,不像现在分得这么清,现在的官方学术和民间学术甚为悬殊,而当时则是融合为一的。孔子就是第一个私学的教师,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的学术还是照样发展,并与官方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地讲学,自由地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地选择。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而教化的基础就在民间。民间学术的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僵硬性的一种力量。
(五)社会礼仪的重建
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又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能够对人的教养和社会良性的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此为历代儒家所关注。
中国古代的教化,要因时代变化不断地调整礼仪。朱子对礼特别重视,朱子的礼学有两种:第一种是具有学术性的《仪礼经传通解》,它把《仪礼》和《礼记》结合起来讲,着重点是在古制,比较详明。第二种是《家礼》,《家礼》简便易行,重在当下之实用。《通解》则极尽其详,多存古制。朱子《家礼序》云: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也。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
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14]观朱子此《序》之义,大要有三:
一者通说礼之义,“礼有本有文”,此落实于“家礼”,其“本”即“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而其“文”,则落实于“冠、婚、丧、祭”之“仪章度数”。
二者言古代礼制虽备,但因世事变化,多已“不宜于世”,需要加以变通以适宜于当世之生活。
三者据此而变通古今,创为一书,其意在于实现先圣“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而且要对国家筹划“导民之义”有所帮助。
朱子关注民间学术,关注礼仪的重建、调整,这就关乎日常生活。他制定《家礼》,对于礼仪之普泛地在社会民众生活中的落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家礼》卷第一“通礼”首列“祠堂”小注云:
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15]
朱子在《家礼》里有很多变通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这个部分本来应该放在“祭礼”里,但他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古代讲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朱子把“祠堂”放在第一部分内容里讲。在朱子看来,建祠堂而使祠堂维持下去要有田,要分出一部分地来养,这样的话,每一家的旁边都要建祠堂,祠堂都归置好了,这样就把“礼”真正落实到一般老百姓身上。祭祀礼仪,出行、有大事的时候,都要去祠堂告诉先祖和祖先,这就把礼落实到一般百姓的生活里。他的见识非常高,也非常平实。西方讲哲学,开始不是学院哲学,后来变成学院哲学,这一套哲学没有直接关乎社会生活的意义,而是通过不同文化部门,对不同文化部门的影响而影响生活,是间接的,但儒家这一套哲学直接影响了社会生活。礼仪尤其如此。
统合以上五点,大体可以见到朱子和宋儒完成其思想建构的基本路径和规模:
第一,建构道统,以奠定其思想的文化生命之认同基础;第二,重构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系统,以确立其思想的经典根据;第三,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心性义理之学的思想系统;第四,关注民间学术和经典的传习;第五,适时变通,重建社会生活的礼仪形式。而其中的最后两点,涉及民众社会生活,是其思想和价值于社会生活层面的落实。
二、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
朱子提出的这一思想蓝图和达成的途径,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当代学术思想形态需要有因时制宜的建构,这就需要意识到重建经典系统的必要性。每个时代都有经典系统的重建,但并非随意。古人的提法经过千锤百炼的淘汰,经过历史检验,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如“周孔”在经典上对应着“五经”,注重在政治方面;“孔孟”在经典上对应着“四书”,注重在心性修养和教化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天人合一和人性本善。核心的经典会提供一整套完整的义理系统。当代学者也注意到了经典系统重建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说法。就目前来看,这些说法尚未形成当代性的思想视域,从而具有相应的思想高度,对经典重构的看法往往杂而不纯。《庄子·人间世》言:“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一个经典系统或者意义系统应该有它最为核心的东西。其实,在当代社会这一政教分离的生存境域下,朱子“四书”的系统仍然有效,它突出性善论,重视个体心灵的功夫教化,关注民间社会的个体教育,对当代政教分离社会背景下的人文素质培育仍有其意义,没必要对宋儒朱子的“四书”经典系统进行刻意的改作,起码目前没有这个必要。现代学者为了强调政治哲学,而特别突出了荀子的意义,但我们认为,目前还是应以性善论和天人合一为基础,把儒家这套教化理念在现代生活里重新建构起来。儒家是一个教化的系统,每个时代讲的虽是原来经典里面的东西,但它某一个方面会在现实中凸显出来,生产出一套新的思想,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把心性凸显出来,形成理学的思想系统。他这一套思想生产的路径,对当下中国社会思想建构、思想生产起一种启示作用。
其次,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的重构以实现思想上的创造性转化,应该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生产的基本意识。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基本上是从外面现成“拿来”的,这些理论诠释方法虽然表现为一元性,但其解释原则未能与经典本身达到真正差异化对待,导致一种外在的批判标准,而所谓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往往蜕化为某种资料性的整理工作,研究对象仅作为与当下生命不甚相关的历史知识而已。经典诠释传统发生了断裂。可以说,方法脱离了内容。朱子建构的一整套“四书”经典诠释的义理系统,首先是作为接续思想生产与思想史研究的相互共生的立言方式,这提醒我们,方法本身不是独立的东西,方法是要回归到内容,是内容的一种展开。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构成自身系统内容的形式方法。方法回归内容,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自身的时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去找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然后以此问题意识,回过头通过对传统经典系统的重新建构,来转化、处理现代意义的形上学、知识论、道德伦理学说等问题。这样一种形上学、伦理道德回到那个经典系统的整体性之中的时候,中国人所讲的道德学说,就和西方理论不一样,这个道德伦理的系统、形上学的系统、知识论的系统,能够与西方的哲学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但同时它拥有它自身的特点,真正形成属于中国当代自身的系统,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才会有主心骨,才会具有一个创造性的本源,才能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最后,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形上学,是一种哲学,其所关注的核心在教化。这种儒学“教化”的哲学意义,要在人的实存及其内在精神生活转变升华的前提下实现生命的真智慧和存在的真实,以达于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之境;由此,人对真实、真理、本体的认识,亦被理解为一种经由人的情感、精神、实存之转变的功夫历程,而为人心所呈现并真实拥有,而非一种单纯理论性的认知。这使之能够密切关联于社会生活,表现为一个内外统合的生命整体。这就要求学者在经典方面的传习讲论中同时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构成当下的思想世界;而经典的学术研究也在这种不断当下化了的思想视域中,参与着思想的生产。因此,它也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哲学学院化之可能性与努力之方向,即要建构以教化为职能的儒家当代思想形态。过去儒学长期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工作,与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应该注意到民间社会学术形态与社会生活样式的重建,培养学者成为有教养的“中国人”,成为以身体道者。只有儒学当代思想实现了双向建构,即理论和社会生活、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起来,其整体乃能逐渐影响到新的当代思想形态之建立。(本文基于我参加一次学术论坛之讲稿。我近患眼疾,读写不便。本文由我口述,博士生王宇丰录音记录整理补充成文。学生田智忠、许家星也参加了本文的相关讨论。)
仁的“偏言”与“专言”
——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
向世陵
从“偏言”与“专言”的角度解说仁,起初是程颐仁说中一个比较专门的话题,即由他之解《周易》而来的“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1]。程颐之论“仁”,自然是其理论本身的需要,但其渊源,却始自先秦以来儒家对于“仁”这一概念的不同界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仁义礼智诸德关系的认识。鉴于“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理学家对此发生兴趣就是理所当然的。其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
一
《周易·乾卦·彖辞》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等语,这是程颐言仁之“偏言”与“专言”说的源头。在语词上,“乾元”之称,显系将卦名“乾”与卦辞“元亨利贞”之“元”整合起来的结果。《彖辞》称颂乾元伟大,突出的是乾的创始作用,天地万物均凭借乾元而生起。
唐代孔颖达引《子夏传》的始、通、和、正为元亨利贞“正义”,并将其概括为四德。所谓“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2]。德者,得也,乾卦凭借其阳性、阳气的创生作用,使所生的万物秉性和谐并得到了最符合它们自身需要的利益和效果。从而,性气合一的生生流行就是乾卦四德的实质,这也是天地间最大的善。圣人则当效法乾元生生而推行此善道。
不过,就《彖辞》自身而言,却既未言善也不及仁,立足善与仁解四德,是《文言》进行再加工的结果。后者曰: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四德之间,元之长善,实质在长人,而人者仁也,所以善之长便归结到君子的以仁为体和仁爱的普施;其余三德,亨通而合乎礼,必然会有众美之嘉会;物各得其利而不害,体现的乃是义之和谐;而固守正道,则足以成为事之主干。那么,天德一方的元亨利贞,已经演绎成为人世的人伦道德体系,四德由天道进入到了人道。参照孔颖达的疏解,四德又与春夏秋冬相配,体现的是一年四季生长收藏的气化运行。从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3]。人世间的德行均因法天而来。君子仁道充实又博爱众生,所以能成为人之尊长。就是说,“泛爱施生”的普遍关爱作为善或仁德,正是君子效法上天“元”德的结果。
在孔颖达看来,天道的四德流贯于人世实际就是仁义礼智,但《文言》本身只言及仁义礼而并未及智,这如何能与人世之四德相通呢?而且,如果不是死咬文字的话,孟子当年强调的仁义礼智之性已经可说是人世之四德,并有“四端”与之相呼应。所以孔颖达也需要予以衔接过渡。他的解释是“(元亨利贞)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智者,行此四事,并须资于知”[4]。就是说,就元亨利贞落实于政事言,表现为仁义礼信,智在这里不是缺失,而是所有这“四事”的施行,都不能离开智慧的运用。所以,智虽未言,却早已融入仁义礼信之中。
孔颖达之解,显然是以五常来回应四德。事实上,在儒家学者那里,五常与四德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各自对应的天道和解释的侧重有所不同,即相对于木火土金水五行,言仁义礼智信五常;相对于春夏秋冬四时,则言仁义礼智四德。所以,孔颖达能方便地将智加入其中,这就为后人直接以仁义礼智诠释四德做好了基本的铺垫。
二
程颐对元亨利贞四德的解释,自然要借鉴汉唐人士的智慧,因而注意四德与五常的关联。对于其间的关系,他的看法是:
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须要分别出。若仁则固一,一所以为仁。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一作便有)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若以东为西,以南为北,则是有不信。如东即东,西即西,则无(一有不字)信。[5]
程颐把四德五常都收归到性上去说。从性上言“五事”,必然会涉及仁的统一与五常之“分别”以及仁性与爱情等方面的关系,还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信”的问题。在这里,仁作为“一”,实际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仁本身就是四德或五常之一,作为内在之性,发于外便表现为恻隐之心;二是仁又是一个融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整体性概念,能够以一统四,正是仁所具有的品格。至于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意味凡事出以公心,人我一致而无偏爱。但恕道虽说是入仁之门,又毕竟不等于仁本身。问题到最后,其实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与表现于外的“四端”即恻隐等情感的关系问题。四端所以未涉及信,在于它不是必要,因为信是相对不信而言,也不存在信的情感或发端的问题。
程子又说: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礼者别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万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恻隐之类,皆情也,凡动者谓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后见,故四端不言信。)[6]
以“公”解仁,突出了爱人的公平无私和普遍性的品格;义礼智则在表明对对象的把握和处置恰到好处;信却有不同,它只是在确认五常之性的存在。可以说,凡物皆有性,性静而情动,恻隐等等便属于性之发动的情感。同时,性本于天而与人的生命同在,这直接就意味着信(性在人的成立),故不需另言。只有在天性被障蔽即“不信”的时候才会出现信的问题。那么,在程颐看来,五性之中是“仁义礼智”四德必有而“信”可缺,这既可以说是重视信——四德五常都必须是实存而不可少;但也表明,理学家的心性(性情)理论建构,可以不需要信的范畴而建立。当然,这并不会危及信作为五常之一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程颐虽也不少论及五常,但往往是作为过渡,重点已转向对仁之义及与其他诸德关系的考虑。他说: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乾健坤顺之类,亦不曾果然体认得。)[7]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说明程颐根本否定了汉唐诸儒对“仁”之义的解释。仁作为儒学的核心范畴,在程颐之前已有多方面的揭示,譬如恻隐、孝悌、博爱、公正,等等。但是,程颐以为它们都有不完全的缺憾。关键的问题,是要能从“仁之道”中分别出五常来。如果只是讲仁的“兼体”,仁就只能是与诸德相互平行的概念,而否定了其包容和统属的功能。在程颐看来,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如同人的头脑与四肢的关系一样,其主从位置是不应当混淆的。《文言》讲“元者善之长”,并不意味着“元”作为众善之首只是位序的优先,即与随后的亨利贞是并列的概念,而是强调仁具有统属四德的性质,它作为“善之长”而顺序演绎成四德,仁德生生而有全体。故通过八卦来揭示的《易》之大义,就是通过乾元来彰显的生生之仁。圣人则因其“体法于乾之仁”而能“长人”,而“体仁,体元也”[8]《文言》的体仁,归结到圣人(君长)效法于乾元而长人上。
从卦象上说,乾为天,但天又有“专言”与“分言”之别:“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9]就此来看,“天”之一词,如果分从形体、主宰、功用、妙用或性情的不同方面言,可以用天、帝、鬼神、神、乾的不同概念去表述;但若专就“天”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道。“专”之字,在程颐那里有专门、专一、专擅等内涵,“专言”即意味专门集中言,并带有整体而非部分的意义:“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10]与之对应的“分言”,自然是分别就“天”的一个方面特征而言之,这可以从生生流行与横向展开的不同角度去进行揭示。比方,“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11]四德之义的广大,由乾元的“善大”步步引出,“善之长”是仁德,也是贯通四德的最重要的性质。
因而,程颐又说:
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12]乾元的伟大,就在于其所贡献的创始万物之道。四德、五常的意义也都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程颐以五常之仁解说四德之元,立足点可以说是仁的生意。“偏言”就是“分言”,即只就每一德或每一常自身而论,着重在这“一事”自身的性质、表现及特征等等;“专言”在此则不仅有专门集中言之义,更是突出了包容统属的功能。因为不论四德的亨利贞还是五常的义礼智信,都来源于乾元或仁的生气流淌,它们作为不同的德目,各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特色,但终究又依赖并被包含在元或仁的善之统体之中。从而,天地万物、人伦五常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既有主从之分又相互发明、既有整体一贯又有各自特色而不能互相代替的结构。
程颐提出仁义礼智的“偏言”与“专言”说,中心都是围绕仁说话,因为仁事实上具有不同的性能,不可能以一个标准来限定。孟子当年讲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等“四心”而表现为人的不同道德情感及意志行为。这里虽然突出了四德的区分,但它们四者毕竟又构成一个同“根于心”的德性整体,故其区分与总成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孟子终究没有合性理与生理为一的仁的概念,仁主要作为德性、情感存在而非生生之源,所以四德虽是内在的却不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后来韩愈讲仁、义、道、德的顺序递进,仁义已随道德主体的践行而有逻辑地展开,相互间已具有一种有机的关联。[13]到程氏兄弟,随着对《易》之“生意”和“生之谓性”等命题的重新审视和吸纳,生意的流淌已成为他们仁学理论建构必不可少的内在黏合剂。比方程颢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4]
将韩愈的道德仁义代入,“生”所以能作为天地之大德,就在于它在根本上促成了仁之善德源源不绝地生长,并通过天地气运交感而凝聚成各自形体性命的过程,使普遍之善凝聚为个体之性(善)。在此人与天地“一物”的意义上,人之爱人,其实就是人物同一的普遍仁性付诸实现,而不应当自我局狭。人既有禀赋了此必然的生意,恻隐之心的生发就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程颐同样以“生道”定义仁心的发端,认为“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15]。而且,“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6]。恻隐之心的触发,正赖于由生意而来的仁性的发动;而一当仁性发动,乾元生,义礼智诸德遂会因时因地而生成。此一机制颇受朱熹推崇,他称赞道:“程子‘谷种’之喻甚善。若有这种种在这里,何患生理不存!”[17]随此生意而下,“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18]。当然,程颐本人并未有朱熹这样的明确论述,但从其乾元始万物的道理和“体仁,体元也”[19]的原则来说,因生意而有四德的有机整体,也是符合程颐思想的逻辑的。
三
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涵摄宇宙论的生理,重在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已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但是,作为话题的提出者,程颐自己对区分仁之“偏言”与“专言”毕竟没有做出更多的发明,而且本身也存在灵活解释的问题。他留给后来的学者及其仁说理论的,更主要的是一个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或标准。朱熹在与其弟子的交流中对此便多有讨论。例如:
(朱熹)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以气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仁则为慈爱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逊;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问:“如何不道‘鲜矣义礼智’,只道‘鲜矣仁’?”曰:“程先生《易传》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专言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义也在里面;‘知觉谓之仁’,便智也在里面。如‘孝弟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爱而言。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才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20]
春夏秋冬、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可以解释为天(乾元)之生物的过程。“坯朴里便有这底”,说明仁性内在,随其生发和流行于人世,表现为真实可信的四德五常及其慈爱、刚断、谦逊、明辨诸情感品行。但学生的问题也由此开始。即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不说“鲜于义礼智”,这当作何理解?朱熹于是以程颐论“专言”和“偏言”作为鉴别标准去规范孔门的论仁诸说,他为此举过不少例证,就此段论述而言,“孝弟为仁之本”“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等被划归偏言;而“仁者必有勇”“知觉谓之仁”“克己复礼为仁”等则成为专言。
具体来说,一方面,“孝弟为仁之本”“泛爱众而亲仁”之间尽管也有孝亲与泛爱众的差别,但总体都是围绕爱人发论,并不涉及仁与其他德行的关联,故朱熹归之于偏言;而学生发问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言下之意是“鲜矣”也应当包含义礼智在内——这实际上是将仁视作专言。朱熹对此没有直接回答,他在《集注》中曾引程子的“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说明,巧言令色“绝无”仁,或曰仁者绝不会巧言令色。[21]而在此处,由于只是针对“巧言令色”者绝非真心爱人这一事,尚未涉及刚断、谦逊、明辨等其余德行的问题,仁在此与义礼智之间便是并列而非包容的关系,故仍归于偏言。另一方面,智、仁、勇本为一体,《中庸》称“所以行之者一也”,即言一已含三,故归于专言;至于“克己复礼为仁”,由于在克己去私或曰“为公”的氛围下,内在之仁昭显,义礼智本来已融于这一工夫之中,四德贯通为一个整体,故当属于专言的范畴。
不过,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专言”问题,常常又是将其纳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2]的框架中去处理的,体现出他对这一问题更多的思考。如说:“‘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23]如此的分合,可以放在他的理一分殊格局来看,即凡有一物便有一物之理,理虽不可见,但从发于外的爱、宜、恭敬辞逊、分辨是非的行为,可推知它们各自都源于其内涵之理;而所有分殊之理又统一到仁这一总理即心之德中,此种仁包四德的心之德,就是朱熹的“保合太和”[24]。那么,如此的分合就不只是概念的辩解,在现实中,由于仁作为“生理”而发生作用,它实际表现为一体连续的过程。如:
先生曰:“某寻常与朋友说,仁为孝弟之本,义礼智亦然。义只是知事亲如此孝,事长如此弟,礼亦是有事亲事长之礼,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为心之德,则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专言则包四者’是也;‘爱之理’,如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动处便见。有感而动时,皆自仁中发出来。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圆池,池虽不同,皆由水而为之也。”[25]
孝悌是根基性的道德践履,但它之生成又依赖于内在的仁性,并表现为对父母兄弟的亲爱之情;相应地,义礼智分别体现在践行孝悌的适宜恰当、礼仪周全及对孝悌之道的认知把握上。就此分别地看待仁义礼智各自的特性和表现说,都可归于偏言;但是,四德又都依存于心并统一于孝悌的行为,再由孝悌(亲亲)推广到仁民、爱物,使仁的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就后者论,仁作为心之德,已将义礼智包容在内,随事有感而发。不论仁的发作流动怎样表现,如水流成池而有大小方圆,但总之都是同一水所造成,事实上是同一个仁,所以谓之专言。那么,偏言与专言在朱熹又是可以相互过渡的。
因此,偏言和专言,实际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譬如朱熹对“小仁”和“大仁”的分析:“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26“小仁”与“大仁”的比喻不是不可以,因为这有助于认识清楚各自的定位和内涵,但又不能以僵化的态度去截然对待。在根本上,仁只有一个,偏言与专言是从不同层面对仁之意蕴的阐发。所以,对于仁的“偏言”与“专言”问题,“看得界限分明”只是问题的一面,更要注意到双方的相互包容:“说着偏言底,专言底便在里面;说专言底,则偏言底便在里面。”27]如在孟子,说“仁,人心也”是谓专言之仁,因为义礼智本是仁心发散的产物;但同时孟子又言“仁之实,事亲是也”,是特指孝亲这一事,仁又成了偏言。所以“专言”与“偏言”都是“相关说”的。[28]
“相关说”者关联孔子论仁的不同解答,但还有一种情况,即同一句话既可以是偏言又能够做专言,例如前面提及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是归于偏言;但他又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如从心之德的视域去看[29],又可以归于专言。之所以如此,基本点仍在于生气流行,“心之德”便可以是“爱之理”也。朱熹解答说:
“‘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气上看。如春夏秋冬,须看他四时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凉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气之长,秋是生气之敛,冬是生气之藏。若春无生物之意,后面三时都无了。此仁所以包得义礼智也,明道所以言‘义礼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抚使,更无一个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抚也。今学者须是先自讲明得一个仁,若理会得后,在心术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见得此仁,则心术上言仁与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30]
“爱之理”与“心之德”的沟通,需要从一气流行又有四时界限上去看。一方面,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各有其性,凉寒热之性本身不能生物,只有温厚的春气,才是天地生物之心的最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春气温厚又不止于一时,它是流动不息的。在充满生物之意的春气熏陶下,夏秋冬的热凉寒之性被化解,热成为生气之长,凉成为生气之敛,寒则成为生气之藏,一切融入整体的生意之中。不论是观念上辨仁,还是实践中施仁,都能够贯通无碍。从此生意看问题,便能够领会程颢之言“义礼智皆仁也”的意义。朱熹举例是福建路安抚使通常由福州知州兼任,两个职位是同一个人任,对这同一人来说,州之专守与路之巡察,即偏言与专言是整合为一体的。
那么,从根本上说,只要生生不息,便仁德常在。“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31]一切都要归到天地生物之心上说,天地人物的情感发用,都是此心的作用和表现。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关键在能否亲切体验。所以一旦能祛除己私,人的居处、执事、事亲、事兄直至恕物的各种活动,都是仁体的流行。所谓“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2]。
因而,不论是仁的“偏言”与“专言”,还是“爱之理”与“心之德”,重点仍在仁的融会贯通。如果真正明白了“仁”之义,则双方的沟通便不是问题。按朱熹《仁说》的归纳: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33]
朱熹的仁说从《易传》走过来,强调“君子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34]。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元亨利贞,由于仁之生意的不可断绝,仁义礼智四德的一以贯之就是必然的。分别从体用关系说,在体一方,仁包仁义礼智而构成为整体的德性;在用一方,爱恭宜别之情统一于恻隐而无所不贯,相对于“偏言”的特定发明,朱熹可能更看重“专言”的一体流行。不过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熹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四德各自的体用,实际上都可统一到仁德自身的体用关系上。基于生气流行,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学者所以需要在“克己复礼为仁”上做功夫,就在于克尽己私才能使仁性昭显,私欲去而公(天)理显,普天下流行的是同一个温厚生意,无所适而不在。
朱熹对《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
诠释及其意义
乐爱国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此,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并将孔子所言解读为:“只要是主动地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从没有不教诲的。”[1]钱穆《论语新解》说:“束修:一解,修是干脯,十脡为束。古人相见,必执贽为礼,束修乃贽之薄者。又一解,束修谓束带修饰。古人年十五,可自束带修饰以见外傅。又曰:束修,指束身修行言。今从前一解。”[2]显然,钱穆把“束修”解读为“干脯”,类似于杨伯峻。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不同意将“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而是解读为“年十五以上”,并且认为,这种解读与孔子所讲“十有五而志于学”、《书传》“十五入小学”相应。为此,他把孔子所言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3]显然,这一解读,与杨伯峻、钱穆相去甚远。宋代朱熹《论语集注》把“束修”解读为肉脯,但不只是“见面薄礼”,把“束修”诠释为“心”,表达为心意,其中蕴含了许多合理的思想,可以为今人的解读和研究提供启迪。
一、束修:是“礼”还是“十五岁以上”
对于《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西汉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4]孔安国只是讲到“奉礼”而需要“束修”,并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进一步解读。孔安国还在注《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时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伎艺,其心休休焉。”[5]也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解读。
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但是其《论语郑氏注》大约于宋初开始失传。近年来,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研究有较大进展。有学者以《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塔那184号墓72TAM184:18/7(b),18/8(b)《论语郑氏注》之《述而》篇第9、10行为底本,并且结合敦煌文献,认为唐写本郑玄注的原文应该是:“自(始)行束修,谓年十五之时(奉?)酒脯。十五已上有恩好者以施遗焉。”[6]“束修”对应的是“酒脯”。郑玄还在讲到亲朋好友结婚、自己有事而无法前往需要遣人送礼时,说:“其礼盖壶酒、束修若犬也。”孔颖达疏曰:“礼物用壶酒及束修。束修,十脡脯也。若无脯,则壶酒及一犬。”[7]显然,在郑玄那里,“束修”是一种与“酒脯”有关的礼物。
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曰:“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应者也。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贽,至也,表已来至也。上则人君用玉,中则卿羔、大夫雁、士雉,下则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其中或束修、壶酒、一犬,悉不得无也。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贽,行束修以上来见谒者,则我未尝不教诲之。故江熙云:‘见其翘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贽见。修,脯也。孔注虽不云修是脯,而意亦不得离脯也。’”[8]显然,皇侃把“束修”解读为“十束脯”,并且还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与“脯”有关。该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孔颖达虽然在《礼记正义》中说“束修,十脡脯也”,但在《尚书正义》中疏孔安国“如有束修一介臣”时,却说:“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节,此亦当然。”[9]他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为“束带修节”。
南北朝范晔撰《后汉书》,唐代李贤等为之作注。其中注《伏湛传》“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曰:“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10]又注《延笃传》“且吾自束修以来”,曰:“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1]在这里,李贤既讲“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又讲“束修谓束带修饰”,应当是指年十五以上自行束修,“束带修饰”。因此,“束修”是就“束带修饰”而言,而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可见,汉唐时期诸儒解读“束修”,既有如郑玄解读为与“酒脯”有关的礼物,或皇侃解读为“脯”,也有如李贤解读为“束带修饰”,虽然郑玄、李贤的解读与“年十五以上”有关,但都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李泽厚《论语今读》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是依据1943年出版的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所言:“《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2]这段言论实际上来自李贤等注《后汉书》。应当说,无论是李贤,还是郑玄,都没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
清代毛奇龄对“束修”多有研究。他的《四书剩言》说:“《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贽见薄物,其见于经传者甚众。如《檀弓》‘束修之问’,《穀梁传》‘束修之肉’,《后汉·第五伦传》‘束修之馈’,则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问之礼为言。若《孔丛子》云‘子思居贫,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为当也’,此犹是偶然馈遗之节。至《北史·儒林传》‘冯伟门徒束修,一毫不受’,则直指教学事矣。又《隋书·刘炫》‘博学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然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则直与《论语》‘未尝无诲’作相反语。又《唐六典》‘国子生初入学,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则分束帛与修为二,然亦是教学贽物。近儒以汉后史书多有‘束修’字作‘约束修饬’解,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荐管宁‘束修其躬’类,遂谓‘束修’不是物,历引诸‘束修’词以为辨。夫天下词字相同者多有,龙星不必是龙,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强同之,谬矣。试诵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将之而上乎?”[13]在毛奇龄看来,《论语》所谓“束修”,一直以来就被解读为“贽见薄物”,是见面的薄物之礼,同时,汉以后所修史书中所谓“束修”,有些并不是指薄物之礼,而是指“约束修饬”。显然,当时就“束修”是“贽见薄物”还是“约束修饬”,有过激烈争论,而毛奇龄赞同把《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中的“束修”解读为“贽见薄物”。
后来的方观旭撰《论语偶记》,根据李贤等注《后汉书》所引郑玄注“束修”而言“谓年十五以上”,说:“盖古人称‘束修’,有指束身修行言者。《列女传》秋胡妇云‘束发修身’,《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得宿卫’,《后汉·延笃传》曰‘且吾自束修以来’,马援、杜诗二传又并以束修为年十五,俱是郑注佐证。《书传》云‘十五入小学,殆行束修时矣。'”[14]这里把“束修”又解读为束身修行。
刘宝楠《论语正义》接受毛奇龄的说法,认为《论语》中的“束修”为“贽礼”,即见面礼。他还说:“李贤《后汉·延笃传》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注《论语》曰“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郑注,所以广异义。人年十六为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故举其所行之贽以表其年。”[15]也就是说,郑玄把“束修”说成是“年十五以上”,是指“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刘宝楠还认为,“《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曰‘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皆以‘束修’表年,与郑义同”,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束修”是“以约束修饰为义”。因此,刘宝楠说:“后之儒者,移以解《论语》此文,且举李贤‘束带修饰’之语,以为郑义亦然,是诬郑矣。”[16]他认为,郑玄不可能把《论语》“束修”解读为“束带修饰”。
与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于“束修”的解读不同,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是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郑君注如此,汉时相传之师说也”。黄式三还说:“《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笃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异于郑君。然《书·秦誓》孔疏引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为某传束修一介臣之证,是孔郑注同。盖年十五以上,束带修饰以就外傅,郑君与孔义可合也。”[17]显然,黄式三是要说明“束修”为“束带修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还是黄式三《论语后案》把“束修”解读为“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他们都把“束修”看作“礼”,并且与“十五岁以上”有关。但这并不可说明“束修”是就“十五岁以上”而言,不可由此得出“束修”就是指“十五岁以上”。
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根据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黄式三《论语后案》中的有关文献材料,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实际上是把重点落在年龄上,而不是落在“礼”上,这不仅不同于刘宝楠《论语正义》,而且也不同于黄式三《论语后案》,甚至不同于所有把“束修”看作“礼”的解读。把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更像是说孔子在做义务教育。
二、“修,脯也。十脡为束”
继孔安国注《论语》“自行束修以上”之后,皇侃之疏明确讲“束修,十束脯”,“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后来,孔颖达讲“束修,十脡脯也”,北宋邢昺也疏曰:“束修,礼之薄者。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而来学者,则吾未曾不诲焉,皆教诲之也……‘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者,按:《书传》言束修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18]此外,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在论及“束帛、束修之制”时说:“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疋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19]可见,在皇侃讲“束修,十束脯”之后,较多学者认为“束修”为十脡脯,其实只是一束。在数量上有了变化。
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曰:“修,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20显然,朱熹所作的注释,就“束修”而言,与皇侃有一定的相像性。如前所述,在皇侃那里,“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而在朱熹《论语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皇侃讲“束修,十束脯”,朱熹讲“修,脯也。十脡为束”,与孔颖达、邢昺等相同。朱熹还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21]这里所谓“羔雁是较直钱底”,即皇侃所说“中则卿羔、大夫雁”。
其实,朱熹不仅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束修”解读为“修,脯也。十脡为束”,而且还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也同孔颖达《礼记正义》那样讲“束修,十脡脯也”[22]。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在数量上等同于皇侃所谓“束修,十束脯”。
平心而论,朱熹对于《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解读,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过皇侃、孔颖达、邢昺。那么,朱熹的解读,其新意又何在?
以朱熹为首的宋代理学家,其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实际上并不只是停留于字面上,其重点更在于探讨这些字面含义背后的所以然之理,因此,要在弄清楚孔子所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字面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即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朱熹所谓:“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在朱熹看来,之所以要“自行束修以上”,是因为如果没有“束修”,那么就“不知来学”,“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与此相反,“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照朱熹这一解读,孔子之所以要求“自行束修以上”,其目的只是在于表明来学之诚意,并能够据此而有往教之礼;而之所以“未尝无诲”,是因为“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
在《论语》中,孔子讲“仁”,“仁者爱人”;而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则不仅讲“仁”,而且讲“仁者之心”“仁之体”。朱熹注《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23]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指自己欲立达,由此而想到他人也欲立达,这是“以己及人”,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至于仁者为什么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引程颢所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已。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24]也就是说,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朱熹注“束修”所说“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能够“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做到“诲人不倦”。
孔子不仅讲“仁”,而且讲“恕”;而朱熹则不仅讲“以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还讲“推己及人”,并讨论“仁”“恕”之别。朱熹注《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并引述程颢所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25]。认为孔子所谓“恕”,即“推己及人”。据《论语》所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对此,朱熹注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6朱熹认为“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为“仁”,而“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恕”;“仁”为“不待勉强”“自然而然”,“恕”为“推己及人”。
朱熹不仅讲“仁”“恕”之别,而且特别强调“推己及人”为“仁之方”。朱熹《论语集注》在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的同时,又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27]认为“能近取譬”,从自己所欲而推知他人所欲,推己及人,是仁之方。据《论语》所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朱熹注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28]认为孔子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及人”,可以终身行之。这也就是朱熹注《论语》“束修”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因而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也就是说,若能够“自行束修以上”,以礼而来,那么就能知得来学,因而才有“往教之礼”。
三、“束修”之理
孔子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如果把“束修”解读为“干肉”,很容易使今天的人们联想到孔子是把“束修”当作教人的报酬。问题是,孔子肯定不是为了获得“束修”而教人;在一定意义上看,“自行束修以上”只是“礼”,所以孔安国解读为“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汉唐儒家把“束修”解说为或干肉之类的“贽见薄物”,或“束带修饰”,都是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朱熹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29]在朱熹看来,“礼”和“钱”是不能混淆的,而有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才有“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由此亦可推想,李泽厚《论语今读》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并且能够得到一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担心如果把“束修”解读“干肉”,会与教人之报酬混为一谈,而导致所谓“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并与孔子讲“有教无类”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冲突。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束修”,包含了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认为“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但是,在朱熹看来,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不止于“礼”,又超出了“礼”的层面,而是在落实“推己及人”之恕道,也就是说,通过“自行束修以上”便能够知得来学者,而最重要的是知得来学者的诚意,由此才能有往教之礼。
朱熹对于孔子所谓“束修”的解读,重视谢良佐、杨时等人的说法。他的《论孟精义》引谢良佐所说:“束修不必用于见师,古人相见之礼皆然。言及我门者苟以是心至,未尝不教之。”又引杨时所说:“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30]也就说,“束修”不只是“礼”,而是“心”,是来学者的诚意之心。朱熹的理解与此完全一致。为此,朱熹还说:“诸说无他异。”[31]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之后,接着又注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指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32]朱熹还说:“愤悱,便是诚意到;不愤悱,便是诚不到。”[33]在朱熹看来,老师教学生,要根据学生是否有诚意而施教,这与朱熹注“束修”所表达的根据来学者是否有诚意而决定是否行往教之礼,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对于孔子所谓“束修”,既可以从“礼”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礼,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以表达为心意。
同时,由于“束修”的目的在于教学,“束修”之礼和“束修”之理对于教学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束修”之礼,作为“礼”,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外在的。教者为“束修”而教,学者为“束修”而学,“束修”与教学二分,不能真正落实儒家“为仁由己”的“为己之学”。与此不同,“束修”之理,作为“理”,即为心之诚意,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内在的。诚意不仅是教学的内在根本,也是为人之根本,所以,“束修”之理所包含的诚意,与教学互为一体。
因此,朱熹把孔子所谓“束修”解说为“修,脯也。十艇为束”,虽然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朱熹从“理”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理,诠释为“心”,超越了以往只是从“礼”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礼。而且,这种对于“束修”的形而上学的诠释,也是后来学者未能超越的。
四、余论
对于朱熹解读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提出的“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后来的王夫之多有批评。他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己之心而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而安能已于吾心哉!始来学者,执束修以见,则已有志于学,而愿受教于吾矣。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益教者之道固然,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学而上达,存乎其人而已矣。”[34]王夫之认为,教者在于教,而不能不教,这是教者之道,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心”。显然,这是针对朱熹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言。
诚然,就一般道理而言,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二者是一致的。就具体而言,对于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朱熹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王夫之讲“未尝无有以诲之”,二者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对于没有执束修以见,且不知是否来求学者,朱熹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无论是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还是没有执束修以见的非来学者,都必须是“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显然,王夫之对于儒学之道的理解,与朱熹是有一定差异的。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述了历史上各种关于“束修”的解读,也包括清代毛奇龄《四书剩言》、刘宝楠《论语正义》、黄式三《论语后案》的观点,但并没有就“束修”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只是引述《四书诠义》所言:“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而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公之至也。”[35]显然,这一引述大致依据朱熹的解读而来。所谓“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讲孔子无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这与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是一致的;所谓“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正是依据朱熹所言“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朱熹生活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宋代理学追求自我,追求成圣,自我意识日益强大,人们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朱熹重视人与人之间因气禀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尊重他人自己的选择,讲“不知来学,
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这与当时人们强调自我意识,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王夫之所在的明末清初,人们的自我意识日渐弱化,启蒙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夫之强调“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也可见得其合理之处。换言之,儒家在不同文化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体现出内部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儒学来说,其根本宗旨是不变的。先秦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当然,仅仅停留于这些基本原则是不够的。正是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朱熹既讲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又要求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在对孔子所谓“束修”的诠释中,既提出“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的基本原则,又阐发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具体待人之道。相对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朱熹不仅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且还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这不仅在对“束修”的诠释上超越了以往的诠释,而且对于理解儒家的待人之道也颇有新意,同时对于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尊重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相比之下,现代各种解读,大都不是接朱熹而来,也不同于王夫之,而显得较为肤浅。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依据汉唐诸儒的一家之言,把“束修”只是理解为“束修”之礼,不能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为“束修”之理,很容易被误解为孔子教人,需要收礼,需要获得报酬,而不是出于“仁”之理;李泽厚《论语今读》讲“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则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似乎能够克服孔子教人需要收礼、“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误解,体现一种平等的义务教育,但这样的解读,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文本依据。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肖永明
一、问题的提出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携范伯崇、林择之等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九月八日抵达长沙。在长沙停留的近两个月中,朱熹与张栻就《中庸》、“太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与交流。十一月,张栻与朱熹溯湘江而上,同游南岳,随后朱熹返回福建。这次交流与对话,就是反复为后世所传颂的“朱张会讲”。
本来,“朱张会讲”对朱熹、张栻两位学者而言,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当时,朱熹37岁,张栻34岁,两人学术体系都处于正在建构、发展,有待成熟、完善的过程之中,还并不是后人眼中地位崇高的学术大师。从朱熹、张栻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这次会讲的认识和定位也很明确,就是相互切磋、商榷,共同探讨、对话。事实上,当时朱熹和张栻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并无明显差别,同时代很多学者提及这两位学者时,有的先说张栻,后说朱熹,有的先说朱熹,后说张栻,说法并不一致,并没有明显的尊此抑彼的倾向。
但朱子弟子后学为了树立朱子学的权威,强化朱熹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按照朱熹为主导、朱熹地位更高、在会讲过程中张栻更多地接受了朱熹之学的思路对朱熹、张栻的“会讲”加以叙述,在叙述中体现出朱熹、张栻学术地位的高低与社会影响的强弱,这实际上就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一种塑造和建构。随着朱熹地位的不断提高,尤其当朱子学成了学术主流、官方哲学之后,朱子后学的这种塑造和建构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传播,甚至湖湘后学为了突出湖湘之学的正统性、正宗性,表明湖湘之学已经超越了湖湘一隅的地域局限而属于主流学术的一部分,也刻意突出朱熹对张栻之学产生影响的一面,彰显朱熹到访岳麓对湖湘学派发展的意义。这样,另外一面,亦即张栻之学乃至整个湖湘学术在朱熹思想学术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在“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以朱熹为核心、正统、主流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自南宋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精心建构,广为流传,又在历代的流传中不断强化,迄今几乎成为学界共识。[1]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后世居学术界的主流、正统地位并无问题,但这种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南宋乾道三年,即将迈向中年的朱熹,其思想理论建构正在进行,学术体系尚未成熟,其正统、主流的地位还没有确立。从历史角度看,朱子弟子后学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未免有失真之处。
因此,本文试图勾勒出“朱张会讲”的基本事实,同时对历代学者有关“朱张会讲”的叙述加以考察,以此从一个侧面了解按照以朱熹为正统、主流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不断建构的过程。
二、“朱张会讲”中的朱熹、张栻
张栻、朱熹的学术思想都源自二程,真德秀曾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2]这既表明张栻、朱熹的思想同出二程,但也表明经过数代传承之后,他们已处于不同的思想谱系中,朱熹为闽学的传人,而张栻则是湖湘学的传人。作为各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已出现颇多差异。而这种学派上、思想上的差异乃是互相交流吸收、质疑辩论的基础,朱张会讲的必要性即体现在这里。
会讲之前,朱熹、张栻已有过面谈,且多次往来通信,讨论、交流学术问题。朱熹说:“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3]又说:“钦夫尝收安问,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如此。非面未易纠也。”[4]而张栻也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不知何日得遂也。”[5]在与陆九龄谈及朱熹时,张栻很是感慨:“书问往来,终岂若会面之得尽其底里哉!”[61在信件往复过程中,虽然二人都颇有收获,但是也感到,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书信中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讨论,而双方的困惑、分歧,更是需要当面商榷、探讨,由此二人产生了当面讨论、对话交流的强烈愿望。从张栻信中可以看到,他觉得很有必要“会见讲论”,这种想法已经在心中盘桓数年之久。而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也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7]他到湖南,是希望和湖湘学者当面探讨,了解湖湘学者在《中庸》问题上的看法。所以尽管“湖南之行,劝止者多”[8],朱熹还是坚持前往。总之,从缘起来看,会讲是朱熹与张栻几年来共同的愿望,目的在于面对面地、更为深入地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解决理论建构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讲只是他们长时期书信讨论的延续和发展。朱熹不远两千里,从福建来到长沙,既不是挑战者,也不是求教者,朱、张二人是平等的学友关系。
关于朱张会讲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已无法详细考证,从存留不多的文献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他们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庸》之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谈到过,王懋竑《朱子年谱》中也有记载:“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9]从中可看出,朱熹、张栻所讨论的是《中庸》已发未发的问题,而且两人都秉持着自己的思想观点,讨论十分激烈。其次,是关于太极的问题[10]。朱、张分别之时,张栻有诗云:“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全无牛。”[11]朱熹亦有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12]再次,是知行问题,朱熹后来说:“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至,下是终之。故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何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13]
朱熹、张栻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很多共识,彼此都感到有收获。朱熹有不少文字谈到这次会讲:
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14]
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15]
熹自去秋之中去长沙……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16]
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171
朱熹认为张栻“见处卓然”,“议论出人意表”,经过此次会讲,自己的收益很大,内心十分钦佩。
后来张栻英年早逝,朱熹在祭文中说:“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18]又说:“嗟唯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返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19]虽然朱熹在祭文中不免有谦虚之意,但是可以看出朱熹是把张栻当作自己“志同而心契”“相与切磋”的学术知己与友人的。
张栻亦将朱熹当成思想上的良友,在谈及朱熹时充满赞赏:“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发也。”[20]又说:“元晦数通书讲论,比旧尤好。《语孟精义》有益学者。”[21]谈到会讲,张栻说:“剧谈无俗调,得句有新功。”[22]对于讲会之益是充分肯定的。
从朱张二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们互相欣赏,志同道合。二人皆对会讲中切磋与进益深感满意,大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这一点,也正说明张栻、朱熹都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守着各自的立场,不存在谁依附谁的关系。他们在思想上的交流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朱张会讲是两位学友在共同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三、同时代学者眼中的朱熹、张栻
在与二人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朱熹、张栻只有学问方向上的差异,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陈亮就曾对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有一个整体的评价,他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亮亦获承教于诸公。”[23在他看来,三人均为“一世学者宗师”,并无高下之别。这一点也为辛弃疾、叶适所认同,辛弃疾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24]叶适则说:“(吕祖谦)与张栻、朱熹同时,学者宗之。”[25]甚至对于叶适来说,朱张也并无特出之处,只是属于他所认可的儒者圈中十多位学者中的两位。[26]周必大也说:“近得敬夫并元晦与子澄书,亦是如此,窃深叹仰。”[27]这表明张栻、朱熹对他本人而言并无分别,因此对二人同表敬佩。陈亮后来又说:“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28陈亮在这里指出,同为“道德性命之学”,张栻、吕祖谦的主张已有被朝廷所接受的倾向,而朱熹的学说之所以能行而不止,则是因其“强立不反”。这种表述实际已经暗示了时人对朱张二人学说的看法,进而我们也就可以窥探出二人当时在学术上的地位。另外,陆九渊也将朱张二人相提并论,他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29]陆氏在此虽然表达了对张栻的认可,但这可能出于张栻与他本人的风格更为接近的考虑,而且他对朱熹又抱有偏见。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在他看来,二人的地位并无明显差异。不难看出,在与朱、张同时代的人看来,无论是就学术地位还是就学问而言,二人并无高低之分。
不仅同时代的学者有这种看法,稍后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陈亮、辛弃疾、叶适认为朱熹、张栻、吕祖谦是当时天下学者师表,楼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30与之类似,赵善下则指出三人同处于“鼎峙相望”的地位,他说:“圣学之传,惟曾与轲……千载而下,独我伊、洛……其徒丧沦,寂寥靡传。南轩俶悯,裒然为倡。东莱晦庵,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与磋切。扶偏黜异,表里洞彻。”[31]更进一步说,三人能够同为时人所认可,就在于其学问能“自为一家”,正如周密所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32]关于如何“自为一家”,即其各自的特色如何,这一点韩淲曾有过论述,他说:“张敬夫卓然有高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盖张之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33]正是因为三人在学术造诣上各有其特殊之处,故而能为时人所认可。
当时学者还建构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将朱熹、张栻、吕祖谦一起纳入其中。李心传说:“中立传郡人罗仲素,仲素传郡人李愿中,愿中传新安朱元晦。康侯传其子仁仲,仁仲传广汉张敬夫。乾道、淳熙间,二人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伯恭,其同志也。”[34]这种道的传承,丁端祖也有论述:“本朝濂溪二程,倡义理之学,续孔孟之传,而天下学者,始知所适从……又得晦庵朱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复阐‘六经’之旨,续濂溪二程之传,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体,天下均所宗师。”[35]“自濂溪、明道、伊川义理之学为诸儒倡……其后又得南轩张氏、晦庵朱氏、东莱吕氏续濂溪、明道、伊川几绝之绪而振起之,六经之道晦而复明。”[36]方大琮的说法也很相似:“元公在当时号善谈名理……赖二程子阐明之而益大,朱、张、吕扶翊之而益尊。”[37]在他们看来,朱熹、张栻、吕祖谦阐明“六经”之旨,接续周程之道的统绪,都是孔孟、周程之道的传人。
与这一论述稍有差异,也有学者仅将朱、张二人看作是二程道学的传承者,如家铉翁就说:“朱张二先生倡道东南,共扶千载之坠绪,志同而道合,相得而弥章者也。”[38]这一论述,强调朱、张在道统传承之中的作用,却没有提及吕祖谦。尽管如此,以上种种叙述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或朱熹、张栻二人作为周程之道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当一种固定的谱系还未成形,权力还未浸入话语中时,人们表述思想的方式,叙述历史的语言也会相对自由和个性化。虽然南宋士人提及朱熹、张栻、吕祖谦时,多以“朱张”或“朱张吕”来并称,但是其中也不乏“张朱”“张朱吕”的提法。如刘宰说:“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怅怅然无所归。”[39]吕中说:“岳麓、白鹿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回视州县之学,不过世俗之文进取之策,其相去岂直千百驿而已哉?”[40]魏了翁也说:“张、朱、吕诸先生之亡,学者无所依归,诚哉是言。”[41]又说:“二程先生者出始发明本学于道丧千载之余……近世胡、张、朱、吕氏继之,而圣贤之心昭昭然揭日月于天下。”[42]真德秀甚至明确指出“惟时湖湘渊源最正”,在叙述圣人之道的传承时屡次先言张而后言朱:“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濂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43]
在这里,他们的论述都将张栻排在朱熹的前面,称“张朱”。但结合当时学者的整体情况看,“朱张”或“张朱”的提法都很常见。在南宋时期的众多的学者、士人看来,朱熹、张栻,或者再加上吕祖谦,都是孔孟之道、周程之学的接续者、继承人。“朱张”或“张朱”的提法并无区分高下的用意。也就是说,朱、张同为当时的学人所并重,并不存在主次高下之分。
四、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
朱熹在其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提出了道统说,建构了“圣人之道”的传承谱系,他本人也具有自任的意识。南宋后期,众多朱子后学尊崇朱熹,突出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如黄榦就不遗余力地塑造朱熹的道统接续者形象。他说:“吾道不明且数千年,程张始阐其端,晦庵先生为之大振厥绪。”[44]“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45]在他看来,自周以来,圣贤之道一脉相承,孔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传,而在当世,又只有朱子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陈埴也说:“晦翁出于诸老先生之后,有集大成之义,故程子有未尽处至晦翁而始成。”[46]作为朱学三传的熊禾亦说:“道丧千载,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而后此道始大明于世。”[47]有的朱子后学甚至将这种道统意识编入启蒙读物。如《性理字训》说:“五帝三王,继天立极,道传大统,时臻盛治……惟周与程,统接孟子,继以朱子,疏源濬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瞆,宁不率从?”[48]在他们看来,千年以来圣贤之道不传,到宋代才大明于世,而朱子是集大成者。这些说法,大大突出了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道统谱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儒学的核心和精髓,确立儒学传承的正统和主流,从而排斥其他的学派。朱子后学构建的道统谱系,排他性也是很明显的。在他们的道统谱系中,其他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被排斥在外,只有朱熹才是唯一的正统,其他儒家学者都只是支流余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原本同时代学者们关于朱、张并立或朱、张、吕鼎立的说法被修正,朱、张乾道三年的岳麓会讲也有了另外的叙述。
朱熹高弟陈淳谈到“朱张会讲”时说:
至如乾道庚寅中,南轩以道学名德守是邦,而东莱为郡文学,是时南轩之学已远造矣,思昔犹专门固滞,及晦翁痛与反覆辨论,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49]
如湖湘之学亦自濂洛而来,只初间论性无善恶,有专门之固,及文公为之反覆辨论,南轩幡然从之。徙义之果,克己之严,虽其早世,不及大成,而所归亦已就平实,有功于吾道之羽翼。[50]
在陈淳的叙述中,张栻本来“专门固滞”,在会讲中,朱熹“痛与反覆辨论”,终于使得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按照这一叙述,朱熹在会讲中是传道者,是正统和主流的代表。他对张栻施加影响,使张栻弃其“专门固滞”之病,归于正学。而张栻则是被动接受正统思想影响,最后一改旧说,完全接受了朱熹的观点。因此,虽然张栻英年早逝,“不及大成”,但仍然可以作为“吾道之羽翼”。当然,只是“羽翼”而并非吾道之正传,这和朱熹道统传承者的地位是有着根本差别的。
显然,这一叙述与真德秀关于“会讲”的叙述“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51]有了根本的差异。它大大抬高了朱熹在会讲中的地位,把一场学友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变成了代表学术主流和正宗的朱子对处于非主流、非正宗地位的张栻的说服和收编,把会讲的过程中朱、张立场不同却地位平等的各抒己见、激烈论辩,变成了正宗、主流与非正宗、非主流之间的战胜和抵抗。在这种叙述中,张栻放弃了自己思想的立场,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受其思想的支配。对“朱张会讲”的这种叙述方式,体现了朱子后学的道统观念,成为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不光是朱熹和张栻关系被重新建构,与朱熹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被朱子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重新加以叙述。如朱熹和吕祖谦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吕祖谦了解朱熹之学后,“尽弃其学而学焉”[52]。而与朱熹学术旨趣不同、理论建构路径有异的陆九渊则被叙述为朱熹很想“挽而归之正”,但陆九渊固执己见、偏于一隅。“如陆学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文公向日最欲挽而归之正,而偏执牢不可破,非如南轩之资,纯粹坦易,一变便可至道也。”[53]很显然,陈淳基于道统观念而极力抬高朱熹的这些叙述,完全是出于朱熹正统地位塑造的需要,其核心观念就是,唯有朱熹“渊源纯粹精极,真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当今之世舍先生其谁哉!”[54]
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大大抬高朱熹的地位,也使得原本与朱熹一同活跃于南宋学术界的其他著名学者黯然失色。在朱子门人后学的不断努力之下,朱子学逐渐被官方接受,朱熹作为孔孟周程的嫡传,在道统谱系中具有了更加牢固的地位。尽管此时的朱子学尚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随着朱子学地位的逐渐上升,朱子后学这种关于朱子地位的叙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栻、吕祖谦等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成为支脉、旁系。朱子门人后学在叙述“朱张会讲”时,也是基于后世对朱、张地位的认识,按照朱子为主、张栻为辅,朱子为道统正宗和学术主流、张栻为支脉和旁系的理解来建构的。在他们看来,说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是对张栻的充分肯定,正是张栻的“徙义之果”、最终归于朱熹才保证了他“有功于吾道之羽翼”。
五、元代以后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
元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书目。与此同时,朱熹的道统地位也得到不断巩固,众多儒家学者都把朱熹作为道统传人。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学者在叙述南宋学术史时,就进一步突出了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而将张栻、吕祖谦等仅仅作为朱熹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取资对象。程端礼说:“自朱子集诸儒之成,讲学之方悉有定论。”[55]胡助说:“至宋濂洛诸大儒起,唱鸣道学以续其传。南渡朱张吕三先生继起私淑,其徒相与讲贯,斯道复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诸儒之大成。然后圣人之道昭揭日星,诸子百家之言折中归一。”[56]陈栎亦说:“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又次则东莱……则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南轩固不杂,东莱远不及矣!”[57]梁寅则认为:“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亦皆有志于道,而天不假年,独朱子年弥高而德弥劭,是以挺然为一代之宗师。”[58]可见,到此时,在不少学者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朱熹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儒中第一人,张栻等而次之,吕祖谦再等而次之;张栻纯粹不杂,但不如朱熹,吕祖谦则远不及朱熹;张栻、吕祖谦虽然有志于道,但天不假年,学术成就有限,只有朱子年高德劭,堪称一代宗师。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许多士人的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历史叙事的潜意识。这时,朱熹和张栻已经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等次,因此从文献上看,人们提及朱熹、张栻的时候,大多是称“朱张”,而鲜有人称“张朱”。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吴澄对“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发展史上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59]但是他对朱、张会讲的过程中二人角色有另外一番叙述:“朱子初焉说太极与南轩不同,后过长沙谒南轩,南轩极言其说之未是。初亦未甚契,既而尽从南轩之说。有诗谢南轩曰:我昔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及南轩死,有文祭之曰:始参差以毕序,卒烂熳而同流。是晦庵太极之说尽得之于南轩,其言若合符节。”[60]按照这一叙述,则朱熹太极之说乃“尽从南轩之说”“尽得之于南轩”,这就与朱子门人后学所说的朱熹说服张栻,张栻“幡然从之”的叙述截然相反了。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元代朱熹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朱熹为核心的道统意识渗透到士人的观念之中,但仍有学者试图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不同的立场对“朱张会讲”加以叙述。
到明代,朱熹的集大成地位进一步强化,张拭、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杨廉认为朱熹的集大成在于能将“象山之尊德性,南轩之辨义利,东莱之矫气质固有以兼之……谓之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殆非过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61]章懋甚至以反诘的语气强调张栻、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不能与朱熹相提并论:“南渡之后有朱、张、吕三先生焉……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耶!由是观之,其得斯道之传者,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62]李东阳也认为,张栻之学要逊朱熹一筹:“晦翁之学,因有大于彼(张栻),然亦资而有之……由南轩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吾于吾士大夫望之矣。”[63]
对朱张关系的这一定位,也决定了明清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方式。黄衷在《岳麓书院祠祀记》中谈到“朱张会讲”说:“朱张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之义,尝越三昼夜而不合,然卒定于朱子。”64]在他看来,认为“朱张会讲”定论于朱熹。黄宗羲也认为张栻得到朱熹的帮助之后,方能“裁之归于平正”[65]。清代的杭世骏则说:“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66]他强调的是张栻、吕祖谦“取资”于朱熹,并且把朱子置于当时众多学者学术活动所围绕的核心。
可以看出,明清学者关于朱、张关系和朱、张会讲的叙述,实际上只是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相关话语的延续和进一步确立。张栻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道统叙述的一个配角,一种烘托。“朱张会讲”中,朱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张栻是被说服、被矫正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尊崇朱熹的氛围非常浓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远超南宋诸儒之上的时候,个别学者对朱张关系的定位仍然有与众不同之处,把朱、张一同视为道统正传:“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及出为世用,推之以开物成务、致君泽民,将无不可。”[67]这一说法将朱、张相提并论,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对张栻地位的充分肯定。
还有学者对“朱张会讲”也有不同于“卒定于朱子”的说法,认为二人商讨论辩,虽两心相契,但关于“未发”看法一直有差异:“以此观之,则二先生昭聚讲论而深相契者大略可见,而未发之旨盖终有未合也。”[68]也就是说,“朱张会讲”并非朱熹对张栻观点的覆盖和张栻对朱熹观点的全盘接受,而是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求同存异,有同有异。在当时,能够对“朱张会讲”进行如此清醒理性的叙述,实属不易。
六、余论
“事实”在被“叙述”时,不可避免地会着上叙述者的颜色,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叙述”或多或少会遮蔽掉被叙述者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事实”进行叙述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实”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建构的方式既受到建构者个人的立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也与时代学术思潮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变化的叙述中便可以得到印证。从最初学者们普遍地认为二人在当时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有的学者看来张栻的地位还要高于朱熹,到后世众多学者认为朱熹的地位高于张栻、在会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化过程,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朱熹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朱张会讲”所呈现的魅力以及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不会这么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在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过程中朱熹与张栻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影响、双方观点各有保留的事实,不能因此将朱熹最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所呈现的形象植入对发生在其早期的“朱张会讲”的叙述之中。本文所关注的是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朱张会讲”究竟事实如何,这一事实又是如何在历代学者不断的叙述中被建构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朱熹审美观探究
尤煌杰
一、前言
从严格意义而言,关于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究,都会有中西学术传统上的差异,进而引发中国是否有“哲学”或“美学”的论战。但是如果我们从各种学术领域当中,得到钻研其研究对象之究极意义的思想理论,就可以说在广义上,中国的诸子百家一系列发展下来的思想就是“中国哲学”。同理,在西洋美学的传统上极注重美的形上学意义,艺术的界定,以及如何产生美感等问题,形成一系列的美学理论。狭义上而言,中国也没有类似西洋美学的理论。但是,中国一样有各种从自身文化发展的艺术表现,论述艺术与道之关系的理论,品味各种知觉活动的审美鉴赏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广义而言,存在中国美学思想。
中西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关于美的课题的理论,大多来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谈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等到艺术家的地位逐渐受到肯定与重视之后,艺术家们的美学思想才慢慢开展出来。所以关于早期思想家们与美学相关的论述,并没有意图在当今我们所理解的系统化美学理论架构下,有意识地、自觉地发展所谓“美学”理论。我们只能说他们对于从感性方面所延伸的课题,结合其哲学思想,予以根源性的说明与论述。这些论述在起初并无意于专论感性问题以形成一特殊理论系统,但是对后世而言,确实为后来的美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建设的基石。例如: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思想,原来的论述要旨在于说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感性活动的论述,却可用来指导后世的艺术创作活动与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使我们现在可以说有某种“儒家美学”或“道家美学”。
朱熹留下许多优美的诗词文章,也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的论述,并有与弟子们互相切磋讨论的对话记录流传后世。在当年应该也没有所谓“美学”学科的概念,但是因为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而延伸出来的论述,使我们可以在广义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来进行关于朱熹的审美观的探究。这是一种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审美观念。这个审美观念透过经典的传递,可以进而实质影响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以及审美对象之鉴赏者的审美观。[1]
本文对于所谓“审美观”的理解,意指通过感性的觉察进而引发某种精神性的观念或情感。所以“感性”活动是审美活动的首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单纯的感觉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审美活动,但是审美活动必要以感觉活动作为起始。对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而言,都需要感觉活动作为起点。认知活动以分析、抽象、推理等理性运作,将“具体”“个别”的感觉内容,抽取出“普遍”“抽象”的概念,因着这些概念而成为传达思想的基本单元。审美活动以直觉或直观的方式处理感觉内容,将这个感觉内容直接联结到某种情感或观念。如果在审美活动中所引发的情感或观念,愈是普及于多数的人使之可以领受到,愈能产生更大的共鸣。
本文期待能通过筛选朱熹有关上述说明之审美活动的言论,加以整理,并尝试理解朱熹哲学理论和审美观之间的理论关系。笔者阐述的方式,将首先检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有关先秦儒家之审美观的批注,再从《朱子语类》中查找朱子与弟子的相关讨论。之后,也寻找朱熹更具个人特色的审美观。
二、朱熹对原始儒家的感性课题的诠释与讨论
儒家哲学对于感官知觉的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此知觉活动的实在性以及此种活动为后续的理性活动提供的一个思想基础,对于知觉活动所提供的内容并不怀疑。
1.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朱熹注:
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观,比视为详矣。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察,则又加详矣。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焉,于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2]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所以,只是个大概。所由,便看他所从之道,如为义,为利。又也看他所由处有是有非。至所安处,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须着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个道理。[3]《论语·为政篇》“观其所以章”本旨是讨论伦理行为的考察与目的,但是
其阶段历程,就其感性活动面而言,亦有可以扩及一般非伦理行为的描述。首先在孔子的言论中,把“视”“观”“察”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与视觉有关的活动。朱熹批注:“观,比视为详矣……察,则又加详矣。”从视觉活动来说,后者比前者增加了更多有意识的聚焦活动,只是在伦理行为的观察上,其聚焦的对象分别是“所以”“所由”“所安”。所“以”是外在可见的“行为表现”;所“由”是“发动行为的内在意念或动机”;所“安”是“享受行为所带来的效果”。在孔子与朱子的原始文脉中,明显地在讨论伦理行为的历程与效果。“视”“观”“察”是源自“主体”有意识的知觉活动,而且有逐级提升加密的意涵。“所以”“所由”“所安”是被观察的“行为者”(作为“客体”)产生的外显行为、行为动机、行为效果。
与视觉有关的词汇,除了以上“视”“观”“察”三个动词之外,朱熹也提及“看”“见”。他说:“阴阳五行之理,须常常看得在目前,则自然牢固矣。”[41
又: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他自见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处,此是可乐天理。[5]上引的“看”或“看见”不是指光学原理上的看见,而是事理上的或人生
境界上的看见,亦即是一种“理会”或“意会”。这些与视觉经验有关的词汇,都不是单指生理性的视觉,而是会加上有意识的或具有“意向性”的观看。在以上的引文中虽然多以伦理行为作为讨论的事例,但是其分析的层次仍然可以运用于美感经验的描述中,只是把观看的对象从伦理行为转换为鉴赏对象即可达成。朱熹从经验上的看见“良辰美景”“日用之间”,向上提升到天理遍在四方流行。因此,由单纯的感性经验上的觉知,变成“可乐天理”。这说明从具象的感性经验提升到对遍在流行的大道的直观,会产生精神愉悦。
2.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朱熹注: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6]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石丈问:“齐何以有韶?”曰:“人说公子完带来,亦有甚据?”淳问:“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今‘添学之’二字,则此意便无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证。曰:“不要理会‘三月’字。须看韶是甚么音调,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闻之便恁地。须就舜之德、孔子之心处看。”[7]
“‘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说得泊然处,便有些庄老。某谓正好看圣人忘肉味处,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又举《史记》载孔子至齐,促从者行,曰:“韶乐作。”从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见童子视端而行直。”“虽是说得异,亦容有此理。”[8]
按照朱熹的意见,他首先根据《史记》增补“学之”二字,使一般人断句的“三月不知肉味”,成为“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又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其次,强调“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据此教人“不要理会‘三月’字”,并否定“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的负面看法。
关于“三月不知肉味”或“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两种句读,孰是孰非,其实各有其理由。一般句读的“三月”不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应是表示很长时间的夸示法。而“学之‘三月'”,就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但是除了《史记》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佐证。所以,朱熹下断语“不要理会‘三月’字”,因为“三月”是否为实指名词都对于本章之解释无关宏旨。
本章的主旨在于记载孔子听《韶乐》的审美经验导致“不知肉味”。这一描述对比了“听”韶乐与“知”肉味,两种不同的知觉经验导致在美感层次上的差异。这个例子肯定抽象的、具空间距离的听觉,压倒具体的、直接的官能接触的味觉。朱熹的解释是“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用现代美学的语汇来转述就是在鉴赏一首作品时,必须有“主体”的鉴赏能力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客体”也必须内含相应的质量,在“主客合一”的状态下完成这个美妙的审美鉴赏活动。
附带一提,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从这一段文献,可以分辨出认知历程与审美历程的差异与交互作用。这段记载所显示的是一种推理过程,说明孔子从“一个特定的行为”,推理出“一个作品正在演奏”。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省略推理。但是这两者之间产生关联性的“联结”,即被省略的前提,却是一种源自美感经验的效果。在文字的背后,没有提及的是“韶乐演奏使人视端而行直”。这个推理严格而言,不是正确的有效推理,但是从孔子当时的有限、特殊情境,可以理解其特定的结论。
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朱熹注:
夫,音扶。舍,上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愚按: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91]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体而言。如“‘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人杰问:“‘乐’字之义,释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某谓:“如仲尼之称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旧看伊川说‘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会未透。自今观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泛滥。且理会乐水乐山,直看得意思穷尽,然后四旁莫不贯通。苟先及四旁,却终至于与本说都理会不得也。”[10]
本节引述《论语·子罕》《子在川上》章,但是关于《朱子语类》则引述《论语·雍也》《知者乐水》章,因为后者的讨论更加简洁与周全。宋儒大致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之叹是对于“道体”之伟大的赞叹,而非议汉儒把它解释为“伤逝”(例如郑玄、何晏、邢昺等人的批注被归类为“伤逝”型)。根据朱熹的批注,具体的“水”的千变万化正是抽象的“道体”的具象表现。再回到鉴赏的主体来看,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能拘泥“知者”与“仁者”的根本差异,或“山”与“水”的本质差异。“知者”与“仁者”就如同“水”的激荡或平静,都是水的同体与不同样态。而“山”与“水”在中国的山水观中也是互相包容与互相依赖,以共成“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景观,即是“山以水为血脉……山得水而活……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郭熙,《林泉高致》)。
本章文献彰显具象观察活动,可以引发超越境界的体验。这种历程不只在纯粹学问性的追索历程上显现,而展示出一种超越直观的境界,也可以解释从具象观察一个审美对象而直观天理大道。说明了思辨活动与审美活动,虽然起点与历程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一同指向永恒大道。
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朱熹注: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11]
《朱子语类》的讨论:问“善者美之实”。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与武王仗大义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争多。只是德处,武王便不同。”曰:“‘未尽善’,亦是征伐处未满意否?”曰:“善只说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处看否?”曰:“是。”谢教,曰:“毕竟揖逊与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个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专就此说。”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毕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诵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见矣。乐便是圣人影子,这处‘未尽善’,便是那里有未满处。”[12]
孔子极度称美于韶乐,认为它同时满足了“美”“善”的极致标准,但是对于武乐则只认为它是具有充分“美”的条件,而缺乏“尽善”的条件。在朱熹的诠释上,认为武王的事功不下于舜,但是在为“德”方面,武王是有“未尽善”的。而此“未尽善”不是武王所愿意或故意的,而是就当时的时局有所“不得已”处。这个解释澄清武乐的“未尽善”不是源自武王的征伐行动的动机不善,而是就其行动本身以及反映在音乐上的属性有“未满处”。这个事例说明对于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美”“善”不是等同的,两者可以兼容,也可以分离存在。但是,以儒家的审美标准而言,一件作品必须以“尽善尽美”作为最终极的目标。
三、朱熹在审美上的发展
(一)感官经验的扩增
儒家审美思想对于感性的肯定是确实的,并且重视视觉经验与听觉经验。在许多讨论中多有触及视、听两种经验。《论语·为政》《视其所以》章把视觉经验更加细致地区分为不同的等级,《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章又把听觉的经验压倒味觉的经验。儒家对于味觉在审美上的地位未给予充分的讨论,但是《老子》的思想却是首开先例对其予以肯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第12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35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63章)。《老子》从否定面来看待“无味”之味,扩张了味觉的意涵,延伸它的应用于抽象观念。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论及“味”字共有320段落,对关于“味”的使用有如下各种组合词汇:滋味、玩味、咀味、意味、涵味、无味、知味、熟味、美味、涵泳讽味、余味、忘味、别味、奇羞异味、气味、声色臭味、味别地脉、辨味点茶、味道之腴、诵味、详味、亲切有味、五味、从容涵泳之味、真味。
这些词汇多半出现在讨论读书功夫方面,把有关味觉的词汇使用在知识之追求,我们不能说这些词汇只适用于知识追求,而是应该反过来思考,朱熹大量借用味觉上的动词、名词、形容词来说明如何在读书功夫上精进。而这些味觉上的词汇应该都是源自审美经验的。这种借用的目的最主要在于体验,而不是词类批注。举例来说:
或问:“孟子说‘仁’字,义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晓说,是如何?”曰:“孔子未尝不说,只是公自不会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说糖味甜耳。孔子虽不如此说,却只将那糖与人吃。人若肯吃,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13]
朱熹诠释孔子的教导方式,举例,若要人认识糖的甜味,那就直接给那人吃糖便知道了。这是一种直接体证的方式,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必然经历的方式。
(二)审美范畴的新解
关于审美经验,我们在本文前言就已提及审美经验不只是感觉经验,必须是经过专注、提炼的经验才能成为审美经验。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一则讨论: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只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
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如此,则世间伊尹甚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14]
以上引文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在这个文脉中“目视耳听”之为“物”,因为它们都是个别的知觉经验,未经有意识的筛选,所以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能够把视听的能力发挥到它这个官能的理想境界,或优越境地,也就是耳聪目明,能在知觉中得出一个值得“玩味”“涵泳”的形式,那才符合“则”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朱熹的思想中隐含着审美经验必须从一般感觉经验加以提炼才可获得的原则。
在朱熹的审美思想中,仍然以儒家美学观为主轴而有别于道家美学观,从《朱子语类》有关《邵子之书》可以看出一些分辨。
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人杰因问:“《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犹未离乎害也’。上四句自说得好,却云‘未离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圣人之中道;‘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说前四句。”曰:“性只是仁义礼智,乃是道也。心则统乎性,身则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于物,则身之所资以为用者也。”曰:“此非康节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议论它?”人杰因请教。先生曰:“‘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又问:“如此,则‘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三句,义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耳。”曰:“若论‘万物皆备于我’,则以‘身观物’,亦何不可之有?”[15]
从邵康节的《击壤集序》先提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四句,又提出“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在整个讨论中,前四句被认为可以用儒家观念说得通,符合儒家的基本观念。但是后来修订的七句,被认为倾向道家,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观念。笔者认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从最大的范畴逐层含摄较小范畴,这个“观”的功能就在于连接上层观念与下层观念的隶属关系。这个连接为进德修业、修身养性,产生一种逐层进阶的提升,有助于伦理教化之功,也符合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是“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它不再在乎上下层次的含摄关系。
邵雍之所以舍弃纯粹儒家的思路,在于他点出这层层约制关系中有“未离乎害”,亦即在含摄过程中有所保留与舍弃,而不能保全整体。而“以道观道……”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套套逻辑论式,而是就“道”自身的本质而考究其作为“道”的展现,以下类推。所以他说:“虽欲相伤,其可得乎?”如此,得以保全各实体的整全面貌。
犹如《易·乾卦·彖传》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道是道,性是性,心是心,等等,从一个万事万物作为存有者的角度,各自保有其本质的特征。就如同《朱子语类》中对于“各正性命”的讨论:
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圣人于乾卦发此两句,最好。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都是正个性命。保合得个和气性命,便是当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个皮壳包裹在里。如人以刀破其腹,此个物事便散,却便死。”[16]
到那万物各得其所时,便是物物如此。“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变化是个浑全底。”[17]
因此,再回到邵康节所称许的“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对照《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两者可以相通,不必然要把邵子的思想立即推向道家那一边去。如此“观”字在此的功能要比前段文字的“以道观性……”的应用范围更广泛,既可以说明形上学的存有状态,也可以作为鉴赏活动或审美经验上的一个核心动作。因此,如果朱熹不再拘泥儒家伦理观,而能从儒家形上学的立场来思考,就可以融通邵雍的思想,扩大审美经验的范围与高度。[18]
(三)“悦乐”作为审美经验的最高境界
以儒家的观点人生乐处在于成德,或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朱子语类》提及“孔颜乐处”:
问:“濂溪教程子寻孔颜乐处,盖自有其乐,然求之亦甚难。”曰:“先贤到乐处,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学所能求。况今之师,非濂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着实用功处求之。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久久自当纯熟,充达向上去。”[19]颜回所乐之事不在于“箪瓢陋巷”本身,因为“箪瓢陋巷”其实对于颜回而言,是一种身心的考验,身处于一个物质条件简陋的环境,其简陋足以挠其心志,挫折其志向。而颜回仍然能不改其乐,在于他已经有了体道的经验,其快乐足以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种种不便。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美感经验的追求上,这种颜回之乐,也是符合美感经验的最高境界的。
或问:明道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则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横渠曰:“‘万物皆备于我’,言万事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诚’,谓行无不慊于心,则‘乐莫大焉’。”如明道之说,则物只是物,更不须做事,且于下文‘求仁’之说意思贯串。横渠解‘反身而诚’为行无不慊之义,又似来不得。不唯以物为事,如下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贯得为一意?”曰:“横渠之说亦好。‘反身而诚’,实也。谓实有此理,更无不慊处,则仰不愧,俯不怍,‘乐莫大焉’。‘强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诚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则近于仁矣。如明道这般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20]
对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表示我已无所需求,自身达至完满阶段。而且也不自欺,对自己诚实以对。这是最大可乐之事。综合所述,孔颜之乐在于“忘我”“忘忧”;“万物皆备于我”在于“完满”“充实”;“反身而诚”在于“行无不慊于心”,带来心境上的“心安”。这些源自进德修业的功夫,仍然适用于审美经验,因为美、善境界相合,可以达成“尽善尽美”。
在伦理行为上的“完满”,在于行为本身符合正道,符合人性之自然。在迈向行为的完善历程上,行为者必须借着感性的觉察与理性的判断来修正或验证行为的正当性。当一切符合伦理价值时,行为者感受到行为的完满而享受着实践伦理价值所带来的精神悦乐。而作为一位审美鉴赏者,则是从鉴赏主体默观被鉴赏对象的形象,直观到此形象与大道或“理型”的符合而得到心灵的悦乐。此行为上所践履的“大道”与心灵直观所见到的“大道”是同一的。儒家思想虽没有充分讨论审美的境界,但是由审美鉴赏与伦理实践的共同趋向,可以贯通伦理的悦乐与审美的悦乐,认为两者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我们便可以透过伦理上的悦乐来理解审美上的悦乐所带来的精神境界。[21]
四、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朱熹虽然没有明确地以审美为主题的论述,但是从他对感官经验的描述,可以运用于建立以朱熹思想为依据的审美观。在朱熹的大多数著述中,中心价值在于穷究天理与人性,与师友的讨论也多论及如何行善避恶,或如何读书的方法。整体来看是一种以伦理学为主轴的思想体系,并以天道观作为伦理思想的形上学依据。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也多是如此。但是,如何于人情、人欲上合理安排,仍是实践上必要的课题。经由感性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对美感经验的态度。基于美善同源的理由,我们可以尝试整理出一种儒家式的审美观,以对比于其他思想理论的审美观。
性是理抑或理气合
——朱子、阳明对孟子言“性”的不同理解
蔡家和
一、前言
宋明理学之兴起,其中朱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此因后续者,无论是宗朱或反朱,都多少与朱学相关;朱子继承程子之学而集大成,其编定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学者的必读之书[1],影响所及遍布东亚,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四书”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而朱子结合此四本书,并视此四者为道统的传承: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之后,汉儒无承继,此道统传跳而至程子,而朱子又是此道统的承继者,世称程朱理学。
朱子视自己是正统孟子的承继者,其《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孟子全文逐字逐句地一一注释。在朱子的年代,同时有象山兴起[2,象山属心学,而朱子属理学,双方批对方是禅学;朱子批象山教人不读书,沦为禅,而象山则批朱子求理于外,属义外,是告子之学,在“无极太极”之论辩时亦批朱子杂禅。二人所争辩的,则是谁人能够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真能承继孟子之学?
到了明代,阳明学兴起,亦是反对朱子的义外之说,视朱子格物穷理于外,非孟子的义内之学。阳明学的兴起,则是从其本身体证而来,原本视朱子为圣学的阳明,依于朱子之教而格竹子不得,最终于龙场体悟,发现格物致知原来不离于吾心,于是而有心学的倡议。阳明亦视己才是孟学继承人。此心学与理学的对抗,在《明儒学案》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两派都自认堪为孟学的正统。
本文主要比较朱子与阳明学的不同,并聚焦于二人于孟子性善论之诠解。朱子与阳明对孟子言“性”的见解不同,朱子继于程子,视性为“天理”,而认定孟子之论性而于气有所不备,“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3]。因为性只是理,于气上便有所不足,如朱子言:
《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4]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认为人性与物性于天理处相同,都是仁义礼智,但于气禀的分受不同,人能全其理,而物只能表现其部分。人性、物性皆善,因为都是理,只因气禀的不同而于气质之性上有少异,于是认定在这之中便要加入形气之说始足,而孟子本人则少了此气的转语。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5],一者为天地之性,此性即理,另一性乃此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人性与物性在天理处相同,但在气质之性上始有不同。
以上看出朱子有二性之说,并以性即理为提纲,视孟子的性善是即于天理的性,此性为仁义礼智之性;至于阳明的学说乃针对朱子学而起,朱子学的二元架构,阳明缝补之。朱子将工夫析分为二:先知后行,此知与行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朱子主张体用二元、形上形下二元,以及分判已发、未发为二,凡此,阳明皆一以贯之。[6]
至于“性”的议题,朱子视“性即理”,心可以具理,然心不是理;阳明却视心即性即理。阳明虽也有心即理之说,然而此心即理,是否绝于气呢?阳明视心即理即气,此心并不绝于气,同样地,阳明言性,亦是性即理即气。阳明的原文出处,后文详之。
于此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此一性为天地之性,此中只有理而无气,至于气质之性,为理落于气中所表现出的性,如月印万川,万川所倒映出的月亮,不如本来月亮之光明,此即理一分殊,天理落于形气中而为气质之性。至于阳明的性义,则是把朱子的二元论性义合而为一,以理与气之相合以言性。朱子视性即理,而阳明视性是理、气合,孰是孰非?在此将以孟子的原意来评论。[7]
二、朱子论性
朱子的二性之说始于程子,而朱子集大成而发扬理学,认定孟子于“气”有所不备,此指孟子于气讲得不足而需增补,于是朱子补了形下之气,此为气质、气禀,然此气与理不离不杂,性理与气的相加而为气质之性,乃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者。朱子于《论语》注“性相近,习相远”处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
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
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8]朱子认为,孔子所言“性相近”之性,乃气质之性,而非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有美恶之分,岂能言“相近”?美、恶之相反犹若冰与炭,但溯于其初,还是可谓相近。朱子的意思是,其初不甚相远;美恶者,于其初时并未相反若此。气质之性之所以相差甚多,乃后天之习染所造成,故朱子所言的气质之性,一方面指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另一方面,此气质之性与习相关。然依朱子后的学者,认为气质之性与习应该要做区分,而朱子未有区分,因为性是生而有之,习是后天习染,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两者是该区分。黄宗羲认为:
此章(富岁章)是“性相近习相远”注疏,孙淇澳先生曰:“今若说富岁凶岁,子弟降才有殊,说肥硗雨露人事不齐,而谓麰麦性不同,人谁肯信?至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就形生后说。若禀气于天,成形于地,受变于俗,正肥硗雨露人事类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谓习耳。今不知为习,而强系之性,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9]
黄宗羲注《孟子富岁子弟》章,引孙淇澳的见解,黄与孙两人认为性与习该做区分,性者生而有之,习者,后天也。而朱子把气质之性与习两者混在一起了。然而朱子论性,为何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从程子而来,程子的理由是“性即理”,性是仁义礼智,性之为体,体中也只有仁义礼智,此是性,也是天理,此天理在人,人人相同,不该言相近。而孔子何以言“性相近”?乃因为此处是就气质之性而言,非就本然之性言。故在程朱而言,天地之性,人人相同,都是天理;气质之性,则有美恶之不同,但在其初处,还是相近的。
于此看出朱子对于性的二层区分,有相同之性,此天地之性,性之本也,另一是气质之性,此性与气相混而成。朱子的二层区分,在注释《孟子》的《生之谓性》章处亦表现无遗: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10]
朱子认为,孟子言性是天理,此为形上,此性只有理而无形下之气。至于告子所言“生之谓性”,乃是天之气,而不是理,此为形下。而人物之生,亦有其形上之理,也有形下之气,因为理气不离不杂。此所谓的形上之理,人物皆有之,而人物之不同,在于气禀的差异,人能得其全,物得其偏,此偏、全者,就其能否实践道德之偏全而言,人能道义全具而能实践,动物道义亦全具,然气禀不佳而不能全之,只能表现其偏。
就其气言,人与物都有其知觉运动;就其理言,人物亦都有仁义礼智,但人能全之,物则不能。而人性之所以为无不善,为万物之灵者,乃在于人道义全具,故能付之实践以表现之,动物则只能表现其一部分,不及于人。而告子的差错在于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当之。可见朱子所认定的性可以有两层,上一层为天地之性,此性只有理,而无气,另一层是所谓气性,此气性,如告子所言,以气当之,所谓的生之谓性、食色之性,此所谓的中性材质义之性,而非无不善的本然之性。[11]
在朱子而言,《告子上》的前四章,告子所言之性皆只是形下的气性,未及于形上的必善之性;而于朱子所注的《告子上》前四章,并论及荀子、扬雄、佛氏、告子等人皆如此,所言之性皆是气性,而只有孟子论性是正确的,其视性善之性是形上之性,是天理,而其他人则皆误认气为性,只知饮食男女,而不及于道德。亦是说,荀子、告子等人只知于知觉运动的动物性,此动物性中不具道德性,唯有孟子能够指出道德性。虽人亦有动物性,然孟子不以动物性为性,虽不完全反对动物性,不反对好色、好货之心,然孟子心目中的性乃是以形上之理、道德性为主。
如果再看朱子于《性无善无不善》章所举者更为清楚。朱子举前人之言来做说明,其言: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
这里举了两段程子的话、一段张子的话,都认定性有二,一为天地之性,一为气质之性,而君子以天地之性为第一性,此乃性善之本。又程子之言表示,性与气二者要兼备始可。
然而,这是孟子的本意吗?孟子所言性若早已有气质于其中,则不消如程子一般,言性善若不补个气则为不备(程子先于性中脱落了气质,于是说孟子不备,又自行补上)。孟子的性善若早有气于其中,则不用如程子先把性中的气划分掉,然后说天地之性只有理而无气,因此有所不备,需要再补个气。若是阳明则于性中不脱落气,下文详之。
程子将性与气划分为二,论性,则只是理,而有不足,故要加气以补不足。至于第二段程子的说法,以性与才相比,此性即理,系出于天,而才禀于气,故其定义之才与孟子的才义不同。[13]程子的才是所谓的气禀、气质之性,故程子以性与才作为一相对待概念,其实也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区分。
从以上引文皆可看出,朱子论孟子性善区分了二性,亦可视为程朱理气论的变形,天地之性为理,而气质之性是理带有气。所谓天地之性之为理,亦可言之为理性,或是道德性,至于气质之性则指食色之性、生之谓性等。而朱子以二元区分来看待孟子之性论,阳明并不同意,下文明之。
三、阳明论性
若总结阳明之论孟子性善义,可谓性是理气合,一方面,阳明认为心即性即理,故“性即理”亦可接受,而另一方面,阳明言性又不只是理,尚且是气,故性为理气合。在《传习录·中卷》《答周道通书》有如下对话: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
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
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14]
周道通的疑惑是,程子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不知所指者何?其实,“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有人视为受有禅学“本来面目”影响,如黄宗羲即是如此;“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者,乃指本然之性,此系言语道断,如道之不可道;若一旦可说,则不是本然之性了,而是本然之性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故曰:“才说性已不是性。”一旦说性,则落为气质之性,而不是性之本然矣。而朱子认为,“不容说”者,指人尚未出生之际,尚未具体成为人的气质之性;而曰“不是性”者,乃因不是本然之性,而是本然之性杂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
上引文中,一方面是周道通的疑惑,一方面也是程朱的回答;于此见出,程朱都有两层性论的意思。至于阳明则不然,阳明面对朱子的二元区分,总是缝补之,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缝补;如朱子的工夫之诚明两进[15],阳明则以致良知之本体工夫一以贯之。如今朱子的二性之说,在阳明则以一性通贯之,主张心即性即理。
然而性之即于理,是否即于气?理者,可视为道德之谓;气者,可谓为食色之性等。阳明言生之谓性,生者就气言,所谓的生理欲望、饮食男女等,此语是告子所言,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又谓“食色性也”,而阳明认为此“生”字与气有关,故气即是性,性即是气。至于阳明之解程子“才说性已不是性”,是认为一旦说气即是性时,则仅谈到气性一边,而未有性理。亦是说,依于阳明之见,性即理即气,但若只强调气的一面,则偏于气,而不及理,故不是性之本源;但若只强调本源而不及气,亦不可。孟子之言性固然是从本源上说,乃视性即理,然性只有理而无及于气乎?人性中只有道德,而无形色饮食等乎?阳明也不认为如此,而是性即理即气,理为本,而气为辅,此才是性。
故阳明言性善须在气上始见得,离气也无所谓性。恻隐、羞恶等在阳明视之为气;在朱子也视之为气,是情。然朱子是理气二元,形上形下二元区分,而阳明是理气一滚,形上形下相连。既然阳明言性是理气一滚,又将如何解释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说?
其实这句话,是由朱子真正继承,而阳明也自许可以继承于北宋精神,故其认为有些人只认得性理的一边,而有些人只认得气性一边,这都有所不及。视性为理者,只见道德性,而排斥饮食男女、情感等;视性为气者,却不及于道德。所以最后阳明认为性即气,气即性,性中本有气,非如朱子的先以性即理而排斥了气,最后再补气质之性,把气加回来,而为气质之性。阳明之不同于朱子在于,阳明一开始便不把气排除在性之外,性中本有理、有气,理气相即而为性,性是理气合。于此可见阳明论性与朱子不同,朱子所谓的性善是只有理而无气,而阳明认定的性善是理气相合。
以上讨论了阳明与朱子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见解,以下以孟子原文为标准,视二人谁人得孟子之意。
四、孟子论性
以上二位大儒之相争,对于性的见解不同,然而谁人为正?其实二位儒者都是在诠释孟子的性善论,故以孟子为标准则可判定谁人合于孟子。若如此则必定要回到孟子原文中始可判别。至于一旦谈到孟子的原文时,不知觉地必涉及诠释,本文在此希望尽量少些个人之诠释,而让孟子原文、原意展现出来。接下来,可以先看孟子的《富岁》章: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孟子于此所言的性是什么?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也。”圣人有其人性,一般人也有人性,人与人之间未有不同,圣人能充尽之,一般人亦可充尽之,如同都是麦,若人事稼耕上,其土壤相同,培育时间上相同,则培养出来的结果便能相近。
孟子此章尚有两个重点,第一,孟子言“举相似”,虽孟子于此章亦言“相同”,如“同嗜焉”“同听焉”,但其所谓的相同,应该是相似的意思,如同孟子言“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足之相同,是指其相似,足的大小是相近的,而不会相同;同样的,人的口味亦是相近,而不是相同。
第二,孟子于此所言之性为何?孟子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犬马其性所好的口味,与人性的口味亦不相同,因其不同类所造成,牛好细草,而人则嗜炙,从于易牙之味。故在孟子而言,所谓的人性虽以仁义内在为人性,但人性不止于此,人性如同人这一类的本性,其口之于味者亦是性,故人性中有道德、有食色,此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纵是动物性中,人与动物亦不全同,人好西施,而物不好西施。[16]于此可见,人性中不只有道德性,而是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故孟子言:“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是指口之于味也是人的本性,乃因着运命气数之不齐,而不能必得之,于是君子视此则可有可无,不要求于必得之。
于此而知,阳明与朱子论性,阳明以性是理气合,较符合孟子,而朱子以性即理的看法,与孟子相去较远。朱子补回一个气质之性,也许可弥补此差别,然于本源处,认定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更无食色之性,一分一合之间,已是多此一举。
再举《食色性也》章为例,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如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
告子谈“食色性也”,亦谈“仁内义外”,至于孟子的回辩则只强调义者不在外,而是义内。谓仁内者,孟子也同意,至于食色性也,孟子亦无辩,不只无辩,而且在文末更以饮食来驳告子,看出孟子并不反对食色之性。
整篇论旨,告子视义为外,而孟子视义为内。然而告子所言外者,以义者为外,指道德的当宜者在于外,所谓的“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指的是长者为外在,而不是我能决定的;而孟子认为长之者才是义,非以长者为义,故视为内。何者为内呢?内是指吾人所生而有之者,在于我身上。仁何以是内?乃因仁是爱人,爱人从爱亲开始,故秦人之弟不爱,而吾弟则爱,此亲情血缘之关系,而为内,故仁之为内,孟子、告子都能同意。
至于义者,孟子视之为内,而告子视之为外,因为孟子视长之者为义;而告子视长者为义,因“彼长而我长之”,故彼长者,非于我也,是外在的。而孟子视仁义礼智为内,为性,是生而有之,内在本有的。然孟子论性善为内,为固有、本有,并不只有仁义是本有,而且人性中除了仁义之性外,亦有食色之性,告子承认了食色之性,故孟子以饮食之嗜炙以喻之。[17]内者,本有也,亦是人性,人性中有仁义,亦有动物性的饮食与生理欲望,只是人的饮食与动物的饮食亦不甚相同。人所喜好的是易牙所煮之食,人喜好的是烧烤之炙。而告子于论辩中,以秦人之弟则不爱,以仁为内,而爱自己兄弟;而以长楚人之长,亦长吾家之长,以长为悦,此悦不在我,而在对象,与吾弟之爱为血缘者不同。血缘是内在者故为内,有血缘者则爱,无血缘者则不爱。至于义,则无关于血缘与否,则以外在的长或不长为标准,故告子视之为外。
孟子最后只好举出人性中的饮食亦为内,亦是人性的一环以回辩,无论嗜谁人所做之炙,都喜欢,且此之爱炙者不从外来,而且是生而有之,是人这一类特殊的饮食习惯。亦是说告子认义为外,而孟子以饮食为内以辩之,论辩义内或外者,为何与饮食有关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此“内”的意思就“性”而言,乃生而有之,人性生而有仁义,亦有特殊饮食性,故孟子以此折服了告子。这也说明,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食色,则性是理气混,而以阳明的意思近于孟子。若于人性中把道德性与饮食切割开来,则孟子此章变得不知所云,而之所以有意义,乃在于人性中,道德与饮食男女者皆于其中。
或可再参见《孟子·告子上》的另一章有着相同的义理,孟季子与公都子的对话代表着孟子与告子的对话,其曰: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此场景同于上一章孟子与告子的义内、义外之辩,而如今场景换为学生的论辩,背后所代表者,则是双方的师承即孟子与告子的见解。孟季子的意思,无论是敬弟、敬叔父,或是敬兄、敬乡人,都由外在位置决定,此为外而不为内,这与“彼长而我长之”的意思一样,乃是告子的义外之说,指的是道义的标准为外在所决定,非我内在之决定。外在决定者,之所以敬叔父者,因叔父年纪长,而敬叔父;敬弟者,乃因尸位之故,此皆为外在决定。但孟子的意思是,长之者才是义,而非长者为义,义是愿意恭敬之心,是在我而不在外。最后的论辩,因着公都子之说而折服了孟季子,此公都子亦是承于孟子的精神而来。
此章与上一章如出一辙,谈义内、义外的问题,最后都以饮食之内在而折服对方。表示人性中,仁义内在,此为人性,然人性之内在者,不只是仁义,饮食亦为内在。此饮食之为内在,为告子、孟季子所深知,故告子言:“食色性也。”而且最后孟子以饮食之内在,来证成了仁义亦内在,仁义与饮食,都是人性。如此才足以折服告子、孟季子。此都说明孟子论性中包括了道德与食色。
然孟子亦不反对食色之性,此为内在,何以孟子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章谈到: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孟子对于“生之谓性”的反对,乃因这是以“生”来定义“性”(“性”者,生也),然性是落实于类上的殊义,乃落于此类而为此类之本质,足以区别于他类者,而生则是存活、存在义,范畴较“性”义大得多,故两者不应做比配。白羽、白雪、白玉之白者,是共相;而犬性、牛性、人性,是殊相,三性都不同,不可以共相定义殊相。白羽、白雪、白玉者,如同所谓的“生”,是为共相范畴,都就其白色而提出共相;而生者,都就其存在而言其共相,万物皆生。至于性,则有其分殊性,故万物之性不同,不可浑沦无别于人性、牛性与犬性,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犬性亦不同,人能实践道德,人性善,动物则无,人的饮食之性与牛的饮食亦不同。此乃“生之谓性章”的义理。孟子并不是反对形下气质之性,而是认为“生”与“性”之间关系的不对等,不可混而同之,更不可以生定义性。
除此之外,孟子亦言“形色天性”[18],乃是指人性中道德是为人性,饮食亦是,人的形色亦与他类不同。故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饮食之特殊性,有其身体与他类之不同。人的形色与动物的形色不同,此为天性所赋予。
然而,孟子既然以人性中的饮食为重要,为何又要批评饮食?亦视耳目为小体?孟子对饮食之人曾有批评,原文如下: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
饮食之人而为人所贱者,因其养小而害大,若饮食作为养小而培育大,则饮食也不当被轻贱。所谓大者,大体也,心官也;小者,小体也,耳目之官也。耳目之官不需被反对,耳目之官是在不思而蔽于物时才有恶。恶是习所造成(也是从于小体所造成,此从者,心官从之)[19],本该性善,形色天性皆为善,耳目之善乃能听从于大体而做善事,如今因蔽于物,为习所染,故有恶,而恶者非耳目之官所该负责,而是蔽于物所造成,是习染所带坏,即因此心官不思而接受恶的习染所致。所以孟子此段最后言:“饮食之人,无有失也。”若饮食之人无失,无以小害大,则饮食之滋养却是应当的。孟子亦饮食,唯其饮食不以小害大,大者,心官之思诚而有德,而饮食正好用以照顾身体,用以实践道德,不妨害大者。饮食、食色者,亦是人性的一环,不可偏废。
面对齐宣王所言“寡人好色、好货”等弊病,孟子的回答是:“于王何有?”其认为好色又何妨,有此则能有其同理心。人这一类的人性就有其人性上的生理需求,此生理需求亦不同于动物,人好西施,动物则不好。于此好色处指点其为人性,则百姓亦为人,亦有人性,则亦需要结婚,故孟子指点若能推己及人,以同理心体会民心,则能行王道,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由此人性而能推己及人,透过小体用以实践大体。
形色都是睟面盎背的表现,形色即于天性,天性中的道德因着食色而能养,而能表现,此即孟子性善论之正义。性者,身体与道德都结合于其中,理气合于其中。若如此诠释孟子的性论,则可知,朱子、阳明对于人性见解的比较,则阳明以性是为理气合的说法较合于孟子,至于朱子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掉,而说孟子不备于气,然后又帮孟子补一个气质之性,可谓多此一举,虽无大错,然一分一合之间,性义枯矣。
五、结语与反思
本文讨论孟子的性义,以及朱子与阳明二人相关诠释何者较合。朱子与阳明常都用自己的体系套于经典,迁就古人以合于自己,可谓“六经”皆我脚注!而本文在此只谈孟子的性义,其他省略。文中谈到,朱子视性即理,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悌,更无食色之性,而阳明认为性是理与气的结合(船山也认为性是理气合)。此理者,道德性也,气者,形色也,食色也。而最后判之以孟子原文,以评二人谁能较得孟子原意。文中举了《孟子·告子上》诸章为论证。本文认为,孟子所言性不是只有道德性,也包括食色之性,也包括形色天性,这些都善,动物亦有形色,然不能助之以成就道德,故动物身体亦无所谓善,而人的形色可成就德性,亦为天性,亦为善。而朱子却视性即理,把气质部分去除,阳明则未去除,故阳明得之,朱子未得之。
本文认为,孟子论性之义,为阳明较能合之。朱子之所以认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此有其时代的需求,一方面,需面对当时时代的需要,如魏晋所发展的才性之学、佛学的无明习之说,另一方面,也结合了佛学的贬低食色的见解,然此应非孟子本意。再者,朱子的二性之说也不合于孟子,孟子未有二性之说。又朱子言性,视人性、物性皆可为善,这也是创造性的诠释,孟子的性善是指人性善,犬牛则无,犬牛虽无善,但犬性还是不同于牛性,非可把此二性泛同之。朱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与物的区别是成就道德的全与偏之区别,此亦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朱子对于习的说明太少,系以气质之性言之,无论先天、后天都以气质之性来定义,然性既是生而有之,则与习应有区别,此朱子浑沦之处。
然朱子亦非全错,只是他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除,而后再补气质之性回去,此分合之际,实是多此一举,而性亦枯槁矣。依于原文,孟子其实并未太多反对饮食男女,而是反对不依大体的饮食男女、以小害大的饮食男女,若饮食得其正者,孟子亦正视之,口之于味亦是性,形色亦是天性,此儒家对于食色之看法,而与佛家有别,不用贬低饮食男女之事,只要得正则可。
朱杰人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既热烈又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两位域外学者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位是德国学者苏费翔,一位是美国学者蔡涵墨。
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2010年,他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1]一文。这篇论文的一大突出贡献是,首次揭示了“道统”一词的词源性发展。他指出,早在唐代,“道统”一词即已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2]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朱子是第一个使用“道统”一词的历史公论[3]。此文梳理了朱子以前的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情况,指出,李若水、刘才邵、李流谦都使用过道统一词,他们的时间都早于朱子。苏氏还进一步指出,朱子使用“道统”一词也许和张浚、张栻父子有关。苏氏认为,在“道统”这一名词与概念的传衍、发展过程中,“朱熹的功劳就是把道统说普遍化,对后世影响甚大;自有朱熹才有人使用‘道统’这一简要的口号来推动相关的论述。在朱熹之前,虽然有学者用‘道统’来称呼学术或政治传承之体系,但是这都是偶然的、罕见的现象,并不能说朱熹以前已存在着一个有系统的‘道统论坛’”[4]。2015年,苏氏再次著文论《宋人道统论》。苏氏认为“‘道统’概念在宋代极其重要,又有强烈影响直到今日”[5]。此文的一个重要展开,是讨论了“道统”与“学统”“治统”的关系。他认为,“道统”概念的原始内涵是指儒家师系的传授系统,但它又与“学统”“治统”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大作《历史的严妆》是一本做翻案文章的著作。他所要推翻的历史是秦桧的反面形象。他发明了所谓“文本考古学”的新方法(恕我直言,所谓“文本考古学”,不外乎考据学与校勘学的所有方法与范畴),对我们的史学观与价值观做了颠覆性的解构,他的基本观点我无法苟同。但是他发现了一篇秦桧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所写的碑记。碑记中秦桧使用了“道统”一词:
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6]
蔡氏指出,这篇碑文申明“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7]。必须承认,蔡氏的发现是重要的,他的观察力也是洞彻的。这篇文献的发现,为宋代道统说的发生、发展以及对朱子道统论深层文化、政治背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依据。
二
“道统”一词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学说的传递。
《孟子·尽心下》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8]
一般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清晰地勾画出儒家道统传续的路线图。朱子在此篇之终有两段很长的注文。第一段注先引:“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9]引文完毕,朱子说:
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
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10]
朱子的按语,首先是对林氏对道统下传的悲观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传道的方式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之别,儒家道统的传续“期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就是说,儒家的道统,并不依靠人对人的口耳相传。“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11]朱子认为儒家的道统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不必担心它会失传。他预言“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其次,他又指出,《孟子》一书以孟子的这一段话终篇,一在表明孟子的儒道之传自有其统绪,二在强调此统之传正有待后来者承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不得辞者”这句话。这是说,孟子是个承担历史使命的人,他无法推辞他的责任。仔细玩味,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道统之传做铺垫。
韩愈是又一个对儒家道统传承做出明确界定的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2]苏费翔指出:“韩愈的系统,有当‘君’的圣王,又有当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没有圣王与贤臣互补关系(皋陶、伊尹等贤臣)。这样很明显分为治统(周公以前)与学统(孔子以后)两个阶段。”[13]
正如苏氏所指出的,无论是孟子的系统,还是韩愈的系统,乃至唐宋人有关道统传授系统的描述,都有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紧张:有位与无位。[14]如苏氏所言,在孔子之前,治统与学统是统一的,但是孔子之后,治统(有位之君臣)与学统(无位之圣贤)是分离的。这样的紧张,必然会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以宋代而言,君臣争夺道统承续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李若水,字清卿,北宋徽宗时人。他认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道统的继承人:“艺祖以勇智之资,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15]
李心传《道命录》卷二《范致明论伊川先生入山著书乞觉察》:“臣闻私议害国,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说诬民。处士横议,亦圣人之所不容。谨按通直郎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劝讲经筵……有轻视人主之意;议法太学……以变乱神考成宪为事。”[16]所谓“轻视人主”“议法太学”“变乱神考成宪为事”,即指妄图取代人主道统之尊的举动。
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是秦桧的碑记。记曰:
臣闻:王者位天地之中,做人民之主,故《说文》谓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为说也。杨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王者之道与儒同宗。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自周东迁,王者之迹熄。独孔圣以儒道设教洙泗之间,其高弟曰七十二子。虽入室升堂,所造有浅深,要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
共成一王之业,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纵之圣,系炎正之统;推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烬。
而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前未遭宋魋之难,讵肯易言之。
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方日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
绍兴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益国公臣秦桧谨记。[17]
蔡涵墨在分析这一碑记时指出:“这些引文又打造了基本的历史模拟脉络:上天保护逆境中的孔子,使孔子传承文王的政治、文化遗产给后世诸圣;如今上天再度在外祸与内乱之下护持宋高宗,使高宗得以再建‘道统’。”“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18]
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道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也注意到“道统”问题的特殊作用。他认为,北宋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这背后则是“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19]他认为,道学家建立“道统”说,是为了用“道”来范围“势”(位)。这“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积极方面则是引‘势’入‘道’。后一方面更是宋代理学家所共同寻求的长程目标”[20]。
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朱子的《中庸章句序》可以发现,朱子在历数道统传承的统绪中特别强调孔子以前都是“圣圣相承”,而“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21]。这是一句惊世骇俗的宣言,他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了尧舜之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序中把孔子之后的传承者一律归于“无位”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22]很显然,朱子是在刻意地把“道”与“势”做切割。如果说,在北宋,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是在觉醒的话,那么,到了朱子(南宋)应该是已经成熟了。
三
在朱子的道统谱系中,二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庸章句序》曰: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23]
这段论述,给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1.孟子以后,程氏兄弟是接续道统的人;
2.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
3.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
4.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们试着来分析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朱子认为程氏兄弟是道统的接续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朱子不是第一人。在朱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这一观点:
刘立之:“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孑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24]按,刘立之,“字宗礼,河间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与二先生有旧,宗礼早孤,数岁即养于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称其登门最早,精于吏事云。”[25]刘氏既为程颢最早的学生,则此说当在明道生前或死后不久。
朱光庭:“自孟轲以来,千有余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著,其闻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26]按,“公讳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师人……嘉祐二年登进士第……绍圣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初,受学于安定先生……后又从程伯淳、正叔二先生于洛阳。”[27]朱氏之论,当在程颢去世不久。但是,朱氏在程氏生前即已持此论,详见后引。
范祖禹:“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28]按,范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为给谏讲读官”[29]。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荐程颐,左正言朱光庭曰:“先生乃天民先觉,圣世真儒。”“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传。”[30]这说明,在二程兄弟生前,即已有传孔孟圣道之名声。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如游酢、吕大临、胡安国等。可见,这种说法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而将二程兄弟明确定义为孔孟之道接续者的,是程颐本人。程颢去世后,文彦博为其墓题碑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程颐为之作墓碑序曰: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国太师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慭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总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世而长存。勒石墓旁,以诏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31]
程颐的碑序十分重要,它既借文彦博之口明确了程颢是明孔孟之道之人,又借梳理道统传续之统,确立了程颢是道统当之无愧的继任者。在《明道先生行状》中他又说:“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32]这是说,程颢具有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
二程为道统的主要承续者,因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而成为定论,被学术界、思想界广泛接受。将二程定为道统的承续者,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道学(理学)在儒家道统传续的整个谱系中的正宗与主导的地位。从此,关于道统传承的各种纷争归于一统,道学在整个儒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道学家也取得了关于道统乃至整个儒学系统中的话语权。
为了构建以二程为宗主的道统谱系,朱子还编著了另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束景南认为:“朱熹的学派道统的正式确立是以《伊洛渊源录》一书为标志的。”[33]《伊洛渊源录》一书,构思于乾道九年(1173),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34]信中明言“周、程以来诸君子”,可见是为了谱叙传道之统。同年,朱子又为好友石墪《中庸集解》作序。序曰:
《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35]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朱子道统思想的建构此时已基本完成,并欲公之于众。但是《伊洛渊源录》一书却受到吕祖谦等人的非议。[36]朱子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37]于是朱子弃《伊洛渊源录》而以《中庸集解序》和《中庸章句序》为言,正式揭示出他的道统理论及谱系。
第二个问题: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这个问题包含着两层内涵。其一,朱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纠缠于文字训诂而不及义理:“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38]这样的学风,自然无法领悟到先圣思想的真谛。其二,“道在目前,初无隐蔽,而众人沉溺胶扰,不自知觉,是以圣人因其所见道体之实,发之言语文字之间,以开悟天下与来世。其言丁宁反复,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岂有故为不尽之言以愚学者之耳目,必俟其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哉?”[39]这就是说,道统的传递,固然离不开“言语文字”,但,言语文字并非靠“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诚如上文所说,朱子在这里强调了儒学道统的超越性和永恒的价值,这就为二程乃至他自己接续道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个问题: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在构建自己的道统理论时,朱子特别警惕佛老对儒学的影响。在建构怎样的道统谱系的问题上,他非常鲜明而坚决地把一切受佛老影响的儒者排斥在外。朱子的道统理论,其实包含着捍卫儒家学说纯正性的战斗精神。
第四个问题: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朱子认为程氏兄弟在道统传续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那么整个道统体系就要崩塌。所以他说“微程夫子”,就不可能得儒学、儒道之心。
四
苏费翔在《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中说:“他的目标似乎就是弘扬自己传道之说。”[40]在《宋人道统论》中,他又指出:“朱熹与孟子、韩愈大有不同,绝不认为今世道统失传,倡导宋初道统复兴之说,谓二程兄弟接续孟子之传,没有说二程之后再失传。可见朱熹很确定他自己是继承人。”[41]其实,在苏氏之前,已有很多学者指出,朱子似欲以道统传承者自居。[42]
朱子是否以道统的接续者自居?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朱子从不自诩为道统的继承人,但他一直不讳言,要以承续道统而自任。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43]
可见,朱子从小就立定了为先圣代言立言的志向。
在《中庸集解序》中,他说:
熹之友会稽石君墪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为一书,以便观览,名曰《中庸集解》……熹惟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言之详矣。熹之浅陋,盖有行思坐诵,没世穷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辞于其间!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熹诚不敏,私窃惧焉,故因子重之书,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则为有以真得其传。[44]
《中庸章句序》则曰: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耳。[45]
二序所言,均很自信和肯定地告示,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与注释是得到了先圣的真谛,他的目的就是要传道——使后之学者“或有取焉”。
在《大学章句序》中,他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46]在这篇序中,他明白无误地宣告,《大学章句》中有他自己的思想(正如土田健次郎所言“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张己说”)。但是这篇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熹“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他更明言:“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为务。然其所以言之者,则异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47]我们联系朱子在《孟子》全书结尾处的两段注文,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无疑是宣告了自己就是二程夫子的继任者。于是,道统的谱系最后一环就扣上了,也就是说,有宋一代的道统谱系最后完成了。
但是,自二程到朱子,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为什么继承二程道统的不是别人呢?朱子指出:“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二夫子于此既皆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记平居问答之辞。”[48]这是说二程的道统学说因没有著作留存,而仅靠他们弟子的著述得以流传。但遗憾的是,他的弟子们“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491。所以朱子非常感叹地说:“呜呼,是岂古昔圣贤相传之本意,与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50]更使朱子不安的是,程子的门徒们,依然受到佛老的污染而“不能无失”:“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51]于是,捍卫孔门道统的纯正,就成为朱子当仁不让的使命。
绍熙五年(1194),朱子65岁,辞官归乡,建沧州精舍,作《沧州精舍告先圣文》:
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维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援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载钻载仰,虽未有闻。赖天之灵,幸无失坠。逮兹退老,同好鼎来。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传之方来,永永无斁。[52]
此文为朱子晚年所作,可说是朱子关于“道统”说的一个总结性文献。在这篇并不很长的告文中,朱子再一次清晰地勾画了儒家道统的传续谱系,并自述了在传承道统的事业中自己的认识与作为。他自认为对先圣的道统精神已做到了“探原推本,敢昧厥初”,从此以后,道统之传将“传之方来,永永无斁”。这篇告文,充分显示出一个儒者的历史担当与强烈的使命意识。
朱子的道统说,最后的总结是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完成的。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二十一年,黄榦作《勉斋集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黄榦明确提出:“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文章结尾处,他又强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53]。至此,道统的谱系得以明确而清晰地表述,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遂成为定谳,并为学界所接受。
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
朱汉民
孔子及早期儒家通过整理“六经”,为“六经”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伏羲、神农、尧、舜、禹、文、武、周公的道统脉络,奠定了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同样,朱熹及宋儒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分别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论语集注》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脉络,完成了宋儒的道统论思想体系。在《四书集注》诸篇序说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希望继承孔子整理、诠释“六经”而确立儒家道统的思想传统。他主要是通过结集、诠释“四书”而建构理学,同时推动儒家道统论思想的成型。
朱熹延续北宋儒家从人物谱系、思想内涵方面探讨道统传承,尤其是能够从经典文本方面全面确立道统论。“四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经典体系,是因为它们被纳入数千年圣圣相传的儒家经典体系的道统脉络之中。朱熹通过确立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四书”学,同时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纳入数千年圣圣相传的儒家文明传道的脉络之中,实现对儒家道统论的重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就是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重建新儒家的道统论。
一、道统论与“四书”经典体系
考察儒学历史,道统思想总是与载道的经典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要真正实现道统论的重建,就必须把新的道统论与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结合起来。从中唐韩愈重提道统论,到宋初儒家学者倡导不同的道统谱系,道统问题成为宋初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从中唐到宋初,他们的道统谱系没有与相应的经典体系结合起来,其道统论就显得没有学术根基。
朱熹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统一起来。朱熹一生用力最多的是“四书”学研究。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1朱熹一生如此用功于“四书”,确实是因为他认为“五经”记载的先圣道统是由“四书”传承下来的,而他以及理学家群体通过注解“四书”就是传承孔孟道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将道统论与新经典体系即他集注的“四书”联系起来。
儒学文献分为经典、诸子与传记的不同类型,在儒学史上,“经”“传”“子”的区分既是十分明确的,但又是可以转换的。为了推动儒学发展和思想更新,一些由儒家的“子学”著作,可以转变为“六经”的“传”与“记”,“传”与“记”又可能转变为独立“经典”。儒家“经”“传”“子”的文献转换,往往根据的是儒学学术史、思想史演变的需求。为了推动儒学史的发展,汉儒确立和尊崇“五经”体系,同时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子学著作先后提升为传记著作;同样为了儒学史的发展,朱熹将汉代作为传记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提升为独立经典。但是,这不仅仅是文献形式的变换,中间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变化:前轴心文明的先王政典的地位在下降,而轴心时期儒家诸子的著作与思想,越来越居于儒家文献与儒家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
《中庸》《大学》作为先秦儒家的子学著作,已经在汉代编入《礼记》,尽管以后《礼记》也逐渐由传记之学演变为《礼》经,但唐以前《中庸》《大学》均不是独立经典,其思想的内涵、意义与“四书”学区别很大。宋儒开始了重建经典的行动,是由于儒家道统授受脉络,必须通过“载道之文”的经典体系才能够确立;反过来说,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子学著作提升为独立经典,需要一个儒家道统脉络的依据。于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四书”,开始由儒家子学和“五经”传记,逐渐演变、发展为独立经典,并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四书”学经典体系。
朱熹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确立为经典体系,必须确立这四部书是如何承接三代先王之道的。朱熹在“四书”的序说中,说明每一部书在传承三代先王之道的道统论意义。
孔子是儒学的创建者,他是“六经”的整理者,也是先王之道的自觉传承者,他的道统地位是儒家的基本共识。《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讲学的记录,是关于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所以,我们在《论语集注》书前的《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可以看到,朱熹并没有对《论语》这一部书做更多道统论的说明,而主要将道统的代表经典,放到其他三部著作的阐述上。朱熹在《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主要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论述、二程对《论语》的看法,进一步说明《论语》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朱熹在《读论语孟子法》引述程子的说法:“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21这是二程、朱熹的一个重要主张,即《论语》《孟子》是儒家经典之本,这与汉儒以“六经”为儒家经典之本、《论语》只是所谓“小经”有很大区别。他们特别强调了《论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代替“六经”,这就更加强化了《论语》的道统论意义。另外,在《语孟精义序》中,朱熹即称是书“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3],也是进一步说明《论语》一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性。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做了不一般的处理和论证。《大学章句序》,对《大学》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地位,做了特别的强调。一方面,朱熹强调治、教合一在道统史上的意义,他肯定从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先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君师”一体、“教治”合一,这体现出“继天立极”的道脉传承,儒家学说就是继承了上古圣王“教治”合一的传统,朱熹强调“《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4],就是强调《大学》是记载三代“教治”合一的传道之文。另一方面,朱熹强调《大学》一书是孔子传道曾子的重要典籍,他说:“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休,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51朱熹引用程子的说法,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6],故而他将《大学》分成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叙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7]。所以,朱熹从上述两个方面,充分肯定这一部“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的书,既保留了远古以来“君师”一体、“教治”合一的圣王之道,又是体现孔子、曾子二人传道精神的重要文献。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同样做了不一般的论证。在儒家典籍中,一直就有尧、舜、禹在传位的同时也传道的记载。《论语·尧曰》有尧帝语于舜帝之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也载有“允执其中”。以中道作为儒家道统授受的思想核心,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庸》这一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朱熹通过《中庸章句序》以系统阐述儒家道统思想。一方面,朱熹强调“中道”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肯定道统史上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即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8];另一方面,则是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在“不得其位”的情况下承接了中庸之道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而有贤于尧、舜”。孔子是“继往圣、开来学”的重要道统人物,再经过颜子、曾子之传,道统传到了子思,“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9]。由此可见,《中庸》一书在道统史上十分重要,它是代表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又是体现孔子、颜子、曾子、子思传承道统的文本。而且,《中庸》一书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是“子思引夫子之言”[10],其余各章则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11]。因此,朱熹也是从两个方面,肯定《中庸》一书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12]的书,是记载孔子、子思传道的重要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重要地位。
《孟子》原来是子学著作,但是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儒家学者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道统谱系上的重要文献,继而上升为经典。像《论语序说》一样,朱熹在《孟子序说》中,也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对孟子的评价,以及韩愈对《孟子》的看法,说明《孟子》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譬如,朱熹引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所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3]。朱熹还引韩愈的评价:“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14]在《孟子序说》中,朱熹摘录韩愈有关儒家道统传授谱系的论述,突出了《孟子》的道统意义。《孟子》终篇《尽心下》末章载有孟子的一段感慨,历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间隔均为五百余年,他们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但是却不断有后圣继起,他显然是关注孔子之后能否有继之者的重要现实问题。朱熹《孟子集注》即从道统论的立场出发做了解说,他说:“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15]
朱熹因孟子而发的“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的感慨,显然是对孟子千年之后的道统,是否有继之者的现实问题的追问。而他本人之所以会以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的诠释与建构,就是传承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来的道统。事实上,朱熹对孔子以来的士人传道经典重视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三代先王传道经典。
二、“四书”学与道统人物谱系
本来,所谓的“道统”就是指传道的人物统绪。但是,在关于道统的人物统绪问题上,儒家向来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既包括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也包括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孔子以前的道统谱系与儒家“六经”有关。儒家道统谱系依据“六经”中两部不同的经典:一部是《尚书》系统的依据,作为“人君辞诰之典”[16],《尚书》文献的作者从尧、舜、禹开始到夏、商、周的先王,代表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人物谱系;另一部是《周易》系统的依据,《易传》有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经文上下篇,而孔子则作传文以解经,故而早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这两套系统既有相同点,又有重要的差别。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更是存在很大差别,一则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中哪些能够列入道统谱系?二则是儒学创建以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的不同朝代,儒学学术思潮不同,儒家学者旨趣各异,究竟谁才是儒学道统的代表,向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唐宋时期儒家士大夫面临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问题,故而他们特别需要强调、建构一个合乎时代需要的道统论。唐代韩愈的《原道》是道统论的重要文献,这一篇文章的观点十分明确:道统上溯至尧舜,下传至孟子。但是,韩愈在另外的文章中又肯定荀子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不仅仅是韩愈,唐代有许多儒家学者,包括长孙无忌、魏徵、杨惊、卢照邻、裴度等均认同“周孔荀孟”的道统人物谱系。[17]到了北宋初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道统谱系仍然十分多元化,他们对三代先王的道统谱系有互不相同的看法,尤其是对孔子以后能够列入道统人物谱系的儒家学者有大相径庭的见解。譬如,宋初理学先驱孙复、石介提出的道统说,就是在尧之前加上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六位圣王,在孟子之后加进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四位道统传人。而苏轼则提出了由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道统谱系。他提出孔孟之后,“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18]。其实,道统人物谱系的观念,反映了那个时代及其儒家学者的儒学思想状况。宋初道统人物谱系的多元化,体现出这一时期儒学复兴要求的强烈和新儒学思想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随着宋学的不断发展,宋学不同学派争鸣的同时道学思想体系成型,道学派的道统论逐渐成熟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程颢逝世之后,程颐作《墓表》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9]这样,程颐就以程颢直承孔孟,作为圣人之道在宋代的继承者,正式确立了道学派的道统论。在程门弟子的推动下,特别是南宋朱熹、张栻的倡导下,一种新的道统论确立并成为思想主流。
如前所述,程朱学派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确立统一起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中每一本书的作者做了介绍和论述。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推介,因他的序言是为了确立一套新经典体系,而确立新经典体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这些书的作者纳入上古时期的道统谱系。“六经”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是由三代圣王的道统人物而“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诸序中,对每一位作者做出说明时,势必会将他与道的授受脉络联系起来。“道统”这个词在朱熹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但是,真正赋予这个概念完整的道统论意义,特别是将道统的授受谱系与经典系统结合起来,还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在《中庸章句序》中使用了“道统”,并且从几个不同方面对其做了详细论证,因此朱熹被学界看作是宋学道统论的真正完成者。
我们进一步考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序言,看他如何建立起孔子以后的道统谱系。为了强化这一道统人物谱系,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道统授受谱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统人物是“君师”合一的上古圣王,他们创造了“教治”合一的道统。朱熹提出:“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20]既是为了对抗佛教的法统,同时也是为了强调儒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朱熹显然吸收了《易传》的思想,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尧、舜之前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追溯《中庸》的思想渊源,对儒家道统的先王传授做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自上古以来道统便圣圣相传,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21]。在《尚书·洪范》《论语》中,均记载有尧、舜、禹授受“允执厥中”的事实,故而朱熹主要以《尚书》为依据,列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人物谱系。另外,朱熹在《孟子说序》中,也特别引证了韩愈《原道》的观点,即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学说。
第二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及其诸弟子的道统授受谱系,他们均是无“君师之位”却能够兴道统之教,故而是重要的道统人物。朱熹在《论语序说》中引述司马迁的看法,肯定孔子在道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朱熹还在《论语集注》的终篇《尧曰》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孔子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他引述杨时的言论说:“《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22]显然,朱熹在这里引述杨时之言,就是以道统论解说孔子及其《论语》“明圣学之所传者”,即应该从道统的角度“著明二十篇之大旨”。《大学》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这不利于道统谱系的确立。朱熹以《大学》包括孔子的经一章,曾子作传十章,进一步确立《大学》的道统谱系。朱熹肯定曾子是《大学》的作者,主要是从道统论建构方面考虑的。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义,他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23朱子在道统人物谱系上,特别强调孟子的重要地位,在《孟子集注序说》中,朱熹引《史记·孟子列传》介绍孟子生平,重点阐释孟子的道统地位。他说:“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4然后,朱熹又通过引用韩愈、二程、杨时,进一步对孟子道统地位做出充分肯定。可见,在朱熹心目中他们所继承的儒家之道,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上承先王之道。
最关键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宋学人物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诸序讨论的重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将宋代道学学派列入孔孟之道的道统脉络中来,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25]在同样讲义理之学的宋学学派中,程朱道学派特别重视《大学》,他们通过诠释《大学》而建构道学,就具有重要的道统谱系意义。另外,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也特别强调,程朱道学派在传授《中庸》学的道统意义。所以,《中庸章句序》和《大学章句序》一样,均凸显了程朱道学在道统谱系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选的注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集中了汉宋诸儒的注释,但是,朱熹最为重视的是程门诸子的思想。在《语孟集义序》中,朱熹曾经阐明《语孟精义》的原则,就是将二程之说“搜辑条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若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26]。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更是将程门道学之说作为其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其引述特别集中。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四书章句集注》共引用了32个学者的语录,其中居前的为二程及其弟子,占引用总数的一半以上。朱熹“四书”学以二程一派为依归的特点,恰恰体现出朱熹的“四书”学其实就是确立了程朱理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朱熹所述的道统论来看,道统授受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圣王、春秋战国的孔孟、宋代的程朱。这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诸序中论述道统人物谱系的特点。但是,如果从性质上看,朱熹所述的道统论只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即有“君师之位”的圣王道统与无“君师之位”的士人道统,这两种道统虽然有联系,但是其中的区别要特别关注。朱熹及其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心经典,就是突出了士人群体承担道统的重要意义。
三、“四书”学与道统核心思想
“道统”不仅要有传道的经典文献、人物谱系,而且特别关键的是要有“道”的核心思想。唐中叶韩愈在面临佛教、道教的盛行而作《原道》时,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义”。到了宋代,无论是面对儒学外部的不同思想信仰,还是儒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这是努力重建新儒学的士大夫必须解答的问题。
程朱确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就是认同“四书”体系里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体系中每一本书的基本宗旨与核心思想做了论述。早期儒家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共同思想特点,就是在继承三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提升和理论建构,其思想成果体现为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
三代先王留给儒家学者的文化遗产就是礼乐文明,这包括一整套宗教化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思想观念,早期儒家继承和改造了这一套礼仪规范,并且对这一套礼仪规范做出理性化的思想诠释和价值提升,创造出了“以礼归仁”“以礼制中”“以礼为教”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义、中庸、教化为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所谓“以礼归仁”,就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仁”的内在情感情操,以“仁”的道德情操、道德理想去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所谓“以礼制中”,也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中”的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以“中”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和治理方法。所谓“以礼为教”,就是通过道德教化,将“礼”的强制规范制度化解为个体道德自觉与社会优良风俗,以“教”的道德自觉与优良风俗完成“礼”的规范秩序和国家治理。
所以,宋儒所确立的“四书”学,其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他们选择、结集、诠释“四书”的目的,就是传承、弘扬、发展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四书”的每一本书既有对某一价值理念的特别关注与论述,又有对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的整体追求。
《论语》准确而全面地记载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对三代礼乐的先王之道的深刻思考,推动了“礼—仁”“礼—中”“礼—教”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这些核心思想也就是道统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仁道、中庸、教化均有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以,孔子是早期儒家仁、中、教的价值体系的奠基人。但是,如何深化、展开儒家仁、中、教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孔门诸弟子各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思想创造。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特别重视《大学》《中庸》《孟子》,恰恰在于这些早期儒家文献对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中、教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孟子》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仁义。从唐中叶韩愈的《原道》开始,就将孟子推举为孔子道统的继承者,后世始有“孔孟之道”的说法。而且,韩愈《原道》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们传承的道统内容就是“仁义”。宋儒继承了这一观点,朱熹在《孟子说序》中引证了韩愈《原道》以“仁义”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的观点。同时,朱熹又引证程子的观点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27]由此可见,从韩愈到二程、朱熹,均认可一个相通的观点,就是孔子与孟子传递的道统内容就是“仁”和“仁义”。但是,宋儒也发展了这一观点,韩愈仅仅是肯定孔孟之道的内容是仁义,而程朱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不仅包括性善、恻隐等心性论,还包括养气、存心等修身工夫论,这恰恰是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拓展,也是宋儒需要进一步诠释和发展的思想。孟子拓展了孔子的仁学,孟子以人的道德情感为经验基础,通过性善、恻隐等心性论思想,从人的内在的、情感的方面确立了儒家关于仁的核心价值;孟子又以义理之天为超验依据,将仁义与超越性的天道结合起来。另外,孟子还关注君子仁人如何自我修养,故而提出养气、存心等实践仁义的修身工夫论。程朱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就是希望以孟子的仁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仁学的不同思想维度。朱熹在《孟子说序》中重点引证道学宗师二程、杨时对《孟子》一书的见解,因为朱熹就是继承了二程、杨时关于《孟子》一书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仁学的理论化、实践化的拓展。
《中庸》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中庸”。《中庸》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这样一部原本是普通诸子学文献的书,如何能够在唐宋以来上升为核心经典?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这一本书集中讨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即中道;其二,这一本书对中道做了多维度的探讨,有利于中庸之道的哲学提升。可见,《中庸》潜在的思想文化价值决定了后来的地位提升。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是他关于道统论的最重要的文献,也是研究宋儒道统论必引的论著。这一篇文章通篇论述道统问题,将“中”认定为上古以来圣圣相传的道统内容,从而确立了中道在儒家道统授受过程中的特别价值。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说:“盖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28]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乃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亦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统的精神核心。“中”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近的思想来源,“中”是西周“礼”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一个是远的思想渊源,“中”是全面涉及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思维方式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而儒家思想,恰恰是既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也继承了华夏中道思想文化的传统。所以,儒家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追溯到三代时期,就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想象,而是有着久远文化渊源。在儒家的“六经”及诸子、传记中,“中道”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朱熹为弘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道”思想,将其作为儒家道统的内容。特别是提升了《中庸》的核心价值,将儒家中道与心性、天理统一起来。
《大学》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教”。《大学》也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它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核心经典的原因在于它强调了“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崇教传统,彰显了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教”。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强调《大学》之教其实就是体现了三代时期“教治”合一的思想传统,这也是儒家推崇的道统。但是,这一种将德性教化与政治治理合一的思想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体现。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首先就提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29]这一个“教人之法”的《大学》之教,源于“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道统。从上古的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道统脉络的人物,其实均是“继天立极”的“君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虽然无“君师”之位,但是继承先王道统而推行“先王之法”,故而有《大学》经一章留下来。然后通过曾子之传,而将此先王之道传递下来。《大学》只是古代先王的“教人之法”,其教人的内容其实就是《论语》《孟子》《中庸》的相关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所以,《论语》《孟子》《中庸》倡导的价值理念其实均可以纳入《大学》的大框架之中。《大学》是朱熹列入“四书”之首的经典,其理由他曾多次强调:“是以是书(指《大学》)之规模虽大,然其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30]《大学》所以被列为“四书”之首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也是为教)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为“教人之法”“教人之术”“修己治人之方”。至于《论语》《中庸》《孟子》等经典所列的教化论,均可分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朱熹明确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31]《大学》作为儒家为学纲目,将“修己治人之方”统统纳入其中。
朱子的思想蓝图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
李景林 王宇丰
引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一个时代总是有一种思想的生产,而思想的生产构成了一个时代学术的核心。所谓的“生产”,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是继承,我们过去常常说“批判继承”,而传统上讲的思想生产并非如此,主要侧重于文化生命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则是产生一种适合当代的思想,以此为基础而构建出一套适合当下所处时代的学术,这样的学术才能契合当下社会和一般的民众生活。
不过,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了中国当代思想的核心地位,学术则只具有一种客观研究和反映过去历史知识的地位。可以说,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当学术和思想产生分离后,学术就变成一种所谓的客观研究和反映过去的历史知识,就可能沦为列文森所形容的“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的命运。[1]
近些年来,大家逐渐意识到思想生产的重要性,有学者也逐渐地开始注重思想的创造。但是总体来说,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的生产,确实还未真正建立起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形态,而且也还没有为思想的产生做好充足的准备。具体来看,我们在问题意识、核心话题、思想论域、经典系统、致思路径、话语风格以及价值认同诸方面,尚未达成基本共识,未能明晰地找到方向上的共通性。
在中国哲学史上,朱子是一个特别有思想原创力的思想家,是宋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朱子以其广大完备之格局,建构并完成了思想生产的基本途径,为宋代儒学设计了宏阔的思想蓝图。我们可以从朱子有关宋代思想建构的蓝图设计,来对当代中国思想建构所可能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这一方面,做一些讨论。
一、朱子的思想蓝图
汉唐以降,儒学略偏重于社会政治层面、心性修养和精神皈依方面,乃渐次为佛家和道教所操持。一直到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兴起已过百年,孝宗的《原道辨》还在用“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来讲三教之功用,这说明佛教、道教的影响深刻而巨大,儒家只能被挤到“治世”一边,而个人身心修养和精神信仰方面还多为佛老思想所占据胜场。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
儒家如果没有一个精神信仰和形上层面的价值系统来作为其“外王”事业的基础,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即宋儒所面临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形上学的价值系统,这是宋儒的志向所在。宋儒自称其学为“实学”,认为当时熙宁变法的失败,从学术根源上讲,即由王安石之学“祖虚无而害实用”,把圣学的“外王”事业错置于释老的“性命之理”之上所致。[2]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宋儒的“心性义理之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应对释老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的冲击,以接续儒学固有的人文传统,为其“外王”之事业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形上学基础(体)。
朱子作为宋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此时代问题有着深刻的反思,并提出自己的一套应对的方法和路径,其所设想的思想蓝图,亦非常宏伟,可以说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子总结宋代的思想学术,设计了一套道路,或者在反思里构建生产思想的路径,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道统的建构
朱子建立圣道传承和思想学术的谱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代的圣道思想学术传承谱系,简称道统;二是宋代以来的思想学术传承谱系,简称道学之传。前者意在寻根,为儒家思想找到人文精神的历史根源;后者意在建立新统,为思想生产做准备。
道统的观念,起源甚早,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就已经萌生。《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已粗略勾勒出尧、舜、禹三代所传之道。《孟子·尽心下》则又有如下详尽的表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可以看作对这一圣道传承观念的一种表述。《论语·里仁》记载孔子有“闻道”之说,而在这里,孟子有关“闻而知之”和“见而知之”两种“知道”方式的区分,源自孔门后学,表现了一种圣道传承的观念,可以看作后儒道统观念之滥觞。[3]另外,我们从简帛《五行》“闻而知之者圣”与“见而知之者智”两命题,参照《礼记·乐记》的相关论述,可知先秦儒家认为文化、文明创制演进过程有“作”与“述”这两面之人格担当者。这一圣道传承论,特别强调“闻而知之者”对于圣道传承之贯通天人的原创性作用。
汉唐以来,一方面是儒家固有的“性命之学”的湮灭,另一方面是佛老的盛行,士人学者都到佛老思想那里去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据。李翱概括当时思想状况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4]由是,韩愈《原道》提出了他的道统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
按照韩愈的理解,儒家的“道”有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子、孟轲一贯下来的传承系统,称作“道统”。他认为,在孟子以后,这个性命之道就失传了。韩愈的这一道统说,大体为宋儒所接受,并继续弘扬。到了朱子那里,则明确而系统地阐述出来,《中庸章句序》云: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6]
朱子历述尧、舜、禹、汤、文、武(君),皋陶、伊、傅、周、召(臣),直到孔子、颜、曾相传之道统,又言道统传至孟子而后失其传。此所传道统之内容,朱子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十六字心传”。总而言之,这一“道统”说,其意义在于接续儒家的人文传统,为宋代的思想建构奠定文化生命之认同基础。朱子则自觉地接续这一具有历史根源性的历史人文传统。
另外,朱子还致力于对北宋以来思想(新统)之谱系的建构。在朱子的思想蓝图里,并不是赖其一人之力建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而是特别注重以往学术积累的积极成果,把这些思想资源凝聚成一种问题意识、核心话题、思想论域,并形成新的思想系统。这一点非常典型地反映在朱子和吕祖谦所编的《近思录》里。该书采摭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子书,是一部记述理学思想的著作,被认为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书。我们从这部书的分篇结构,就可以看出宋儒对学术思想内容的理解,这里面也表现了朱子重建宋代学统的努力。《近思录》共十四卷,原无篇名,《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记载了朱子对《近思录》各篇的逐篇纲目的说法:
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7]
显然,这完全是一个“内圣外王”的结构,与《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学说规模一致。清儒张伯行摘录朱熹书成《续近思录》,亦完全仿照《近思录》的体例。其书十四卷篇目如次:
第一卷道体、第二卷论学、第三卷致知、第四卷存养、第五卷克治、第六卷家道、第七卷出处、第八卷治体、第九卷治法、第十卷政事、第十一卷教学、第十二卷戒警、第十三卷辨别异端、第十四卷总论圣贤。[8]
这表现了时人对朱子学内涵的理解。这个学问规模,与先秦儒家是一致的。
如果说自尧、舜、禹、汤以至孟子的道统建构,意在文化认同和传统的接续,那么,对北宋以来的思想谱系之建构,则意在建立有宋一代以来学术思想的“新统”。前者注重在思想文化上的连续性、根源性,后者则注重在当代思想上的生产。这是朱子为宋代思想所勾画的整体画面和进入路径的第一个方面。
(二)经典系统的重构
每个时代的义理不同,面对的问题亦不同,经典系统的内容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经典还是原来那些历史上留存的文献典籍,但哪些是核心的、哪些是外围的,则会发生某些系统上的变化。宋儒思想的建构,首先表现为一种经典系统的重建。其所重经典,则由汉唐儒的“五经”,转向以“四书”为中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
在经典方面,朱子谓读经要循序渐进,应先“四书”后“六经”;“四书”次序,则宜先《大学》,次《论》《孟》,最后《中庸》。在朱子看来,《大学》三纲八目,概括了儒家由心性内圣功夫外显于治平外王事业的一个总的纲领,故为学须从作为圣学入德之门的《大学》开始;《论语》《孟子》应机接物,因时因事而发微言,循此以进,可以收具体而微、融会贯通之效;最后是《中庸》一书,荟萃儒家天人性命学说之精要。循《大学》《论》《孟》,而后会其极于《中庸》,便可建立学问思想的大本大经。由此再进于经史,乃能知其大义,而不致泥于文字训诂。朱子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9]朱子认为,经史包括丰富浩繁的古代制度、礼制方面的内容,这些东西属于一些历史知识,而“四书”才是儒家义理的精要。在朱子看来,“四书”“道理粲然”,易晓易解,但他同时也指出圣贤之言难精,须从精处用力,再读其他书则易为力,难者既精,粗者便易晓,因为后面的功夫里面已立大体,就不易流于偏颇。
从“四书”的系统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从思想义理上,则凸显了心性之学和道德修养的方面。汉唐的时候主要是以“周孔”并称,“周孔”表征意义在政治领域。到了宋代以后则强调“孔孟”,“孔孟”注重在心性修养或人文教化方面。像《孟子》和《中庸》,就涉及非常多的心性之学。第二,从道统意识上,则注重孔、曾、思、孟的传统。周公以前皆为圣王,乃政治上的传承,孔子之后则为学统的建立。
由此可见,一个经典系统的建立,不是随便选择几本书就可以想当然地确立出来。孔子以“六经”教授弟子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以《周易》《春秋》为中心,《周易》凸显了形上学,《春秋》凸显了要正名分,把这两个方面贯穿在“六经”里,则成为一个经典的系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现如今以传授知识为教学目的的教材编写,经典系统更是思想义理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思想精神根底蕴含其中,义理脉络次第分明。
(三)心性义理之学的诠释
宋儒的道学或理学,就是传圣道之学;而此“道”的内容,即是一心性义理之学。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10]这即是以心性义理之学来概括宋儒之学。
汉唐以来,佛老在精神修养方面发展出一整套精微的思想学说,对儒学形成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宋儒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即是以经典系统为理论支撑,来自觉建构儒家自身的心性义理之学。宋儒多有出入佛老的为学经历,故能清醒地认识其心性论上吸引人们目光的地方,并加以批评,从而转化其为儒家的思想性质。朱子曾说:“佛家一向撤去许多事,只理会自身己;其教虽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会。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这下自无人。”[11]朱子在这里主要借佛家理会自我身心之教来批评一些儒者只是“守经”而不从切己处理会的弊病,佛家摒弃人伦而自修,这是与儒家的根本分歧,但是从某一侧面也引出了儒家自身的“为己之学”,自有一套就自家身心上理会的本领。借此形成儒家心性义理之学的自觉意识,逐渐使佛老一直占据着的心性修养领域重新回归到儒家经典系统的话语中来。
总之,宋儒所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绝非空言推论的产物。其所讨论问题,大率亦皆出自经典。诠释原则和思想重心的转变引发了与之相对应的经典系统的重构,通过经典的讲论、经典的诠释重新构建了一套核心范畴。由这些核心范畴建构起来的义理系统,和汉唐有很大不同,比如汉儒讲天人感应、三统三正、更化,但宋儒讲太极、理气、理欲、性命、心性、性情、性气、格致、本体功夫等,这些观念或范畴的凸显,围绕着心性修养和个体人格的养成这一核心话题,构成新的义理系统和新的理论视域,这就是思想的生产。在这种思想生产与经典之缘生互动的动态机制中,经典乃在不同时代获得其意义重构,参与思想的创造进程,成为思想生产的源头活水和生命源泉。
(四)对民间学术的关注
宋儒讲心性义理不是空谈心性,他们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这个“实学”不是后来所讲的事功之学,其所言“实学”:一者言学贵在自得;二者言学不离人伦日用。这便涉及宋代思想学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和落实问题。这个落实,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民间学术的讲论;二是社会生活样式的重建,也就是礼仪系统的重新建构。宋儒特别注重民间的教化,他们要把这一套东西落实到民间,同时也落实到心性,主要是心性的修养和人格的养成,其所重并不专在政治儒学。
宋代的书院非常发达,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说:“宋学形成之近因,则在书院之设立……宋代书院之设,遍于中国,造端实在南唐升元间,而大盛于宋庆历之际焉。”[12]当时书院非常多,有公立,有私立。其著名者,如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四书院。讲学著名者也很多,有齐同文、孙复、胡瑗、石介等。其实宋代的儒者,无论高居庙堂还是置身江湖,大多都在民间、在书院讲学,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胡瑗为北宋第一大教育家,讲授“明体达用”之学,所从学者达数千人之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学者,对当时的学风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宋史·儒林传》所载,当时礼部每年选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其弟子居朝和教授于四方者甚多。仁宗庆历年间,朝廷于京师立太学,下诏州县皆立学,并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教法。这对当时学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实每一个当时的儒者虽在官,既要治理一方,也要教化一方,担当着教化的职责。朱子当然也是这样的,他对民间的学术和讲学非常重视,经常在民间讲学,其在知南康军期间(孝宗淳熙年间),曾兴复白鹿洞书院,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院规,名曰《白鹿洞书院揭示》。《揭示》有五条:
一曰“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二曰“为学之序”: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三曰“修身之要”: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曰“处事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曰“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在院规后面,朱子讲了所制定院规的主要精神,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13]也就是说圣贤之学是非功利的。
中国传统学术传承,有官、私两条线。民间学术的传承,始终是社会教化的基础。当时的讲学,包括官方、民间的教学,官方的讲学也有民间性质,所谓的官方学说和民间学说是合而为一的,不像现在分得这么清,现在的官方学术和民间学术甚为悬殊,而当时则是融合为一的。孔子就是第一个私学的教师,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的学术还是照样发展,并与官方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地讲学,自由地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地选择。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而教化的基础就在民间。民间学术的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僵硬性的一种力量。
(五)社会礼仪的重建
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又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能够对人的教养和社会良性的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此为历代儒家所关注。
中国古代的教化,要因时代变化不断地调整礼仪。朱子对礼特别重视,朱子的礼学有两种:第一种是具有学术性的《仪礼经传通解》,它把《仪礼》和《礼记》结合起来讲,着重点是在古制,比较详明。第二种是《家礼》,《家礼》简便易行,重在当下之实用。《通解》则极尽其详,多存古制。朱子《家礼序》云: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也。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
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14]观朱子此《序》之义,大要有三:
一者通说礼之义,“礼有本有文”,此落实于“家礼”,其“本”即“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而其“文”,则落实于“冠、婚、丧、祭”之“仪章度数”。
二者言古代礼制虽备,但因世事变化,多已“不宜于世”,需要加以变通以适宜于当世之生活。
三者据此而变通古今,创为一书,其意在于实现先圣“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而且要对国家筹划“导民之义”有所帮助。
朱子关注民间学术,关注礼仪的重建、调整,这就关乎日常生活。他制定《家礼》,对于礼仪之普泛地在社会民众生活中的落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家礼》卷第一“通礼”首列“祠堂”小注云:
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15]
朱子在《家礼》里有很多变通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这个部分本来应该放在“祭礼”里,但他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古代讲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朱子把“祠堂”放在第一部分内容里讲。在朱子看来,建祠堂而使祠堂维持下去要有田,要分出一部分地来养,这样的话,每一家的旁边都要建祠堂,祠堂都归置好了,这样就把“礼”真正落实到一般老百姓身上。祭祀礼仪,出行、有大事的时候,都要去祠堂告诉先祖和祖先,这就把礼落实到一般百姓的生活里。他的见识非常高,也非常平实。西方讲哲学,开始不是学院哲学,后来变成学院哲学,这一套哲学没有直接关乎社会生活的意义,而是通过不同文化部门,对不同文化部门的影响而影响生活,是间接的,但儒家这一套哲学直接影响了社会生活。礼仪尤其如此。
统合以上五点,大体可以见到朱子和宋儒完成其思想建构的基本路径和规模:
第一,建构道统,以奠定其思想的文化生命之认同基础;第二,重构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系统,以确立其思想的经典根据;第三,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心性义理之学的思想系统;第四,关注民间学术和经典的传习;第五,适时变通,重建社会生活的礼仪形式。而其中的最后两点,涉及民众社会生活,是其思想和价值于社会生活层面的落实。
二、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
朱子提出的这一思想蓝图和达成的途径,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当代学术思想形态需要有因时制宜的建构,这就需要意识到重建经典系统的必要性。每个时代都有经典系统的重建,但并非随意。古人的提法经过千锤百炼的淘汰,经过历史检验,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如“周孔”在经典上对应着“五经”,注重在政治方面;“孔孟”在经典上对应着“四书”,注重在心性修养和教化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天人合一和人性本善。核心的经典会提供一整套完整的义理系统。当代学者也注意到了经典系统重建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说法。就目前来看,这些说法尚未形成当代性的思想视域,从而具有相应的思想高度,对经典重构的看法往往杂而不纯。《庄子·人间世》言:“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一个经典系统或者意义系统应该有它最为核心的东西。其实,在当代社会这一政教分离的生存境域下,朱子“四书”的系统仍然有效,它突出性善论,重视个体心灵的功夫教化,关注民间社会的个体教育,对当代政教分离社会背景下的人文素质培育仍有其意义,没必要对宋儒朱子的“四书”经典系统进行刻意的改作,起码目前没有这个必要。现代学者为了强调政治哲学,而特别突出了荀子的意义,但我们认为,目前还是应以性善论和天人合一为基础,把儒家这套教化理念在现代生活里重新建构起来。儒家是一个教化的系统,每个时代讲的虽是原来经典里面的东西,但它某一个方面会在现实中凸显出来,生产出一套新的思想,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把心性凸显出来,形成理学的思想系统。他这一套思想生产的路径,对当下中国社会思想建构、思想生产起一种启示作用。
其次,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的重构以实现思想上的创造性转化,应该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生产的基本意识。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基本上是从外面现成“拿来”的,这些理论诠释方法虽然表现为一元性,但其解释原则未能与经典本身达到真正差异化对待,导致一种外在的批判标准,而所谓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往往蜕化为某种资料性的整理工作,研究对象仅作为与当下生命不甚相关的历史知识而已。经典诠释传统发生了断裂。可以说,方法脱离了内容。朱子建构的一整套“四书”经典诠释的义理系统,首先是作为接续思想生产与思想史研究的相互共生的立言方式,这提醒我们,方法本身不是独立的东西,方法是要回归到内容,是内容的一种展开。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构成自身系统内容的形式方法。方法回归内容,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自身的时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去找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然后以此问题意识,回过头通过对传统经典系统的重新建构,来转化、处理现代意义的形上学、知识论、道德伦理学说等问题。这样一种形上学、伦理道德回到那个经典系统的整体性之中的时候,中国人所讲的道德学说,就和西方理论不一样,这个道德伦理的系统、形上学的系统、知识论的系统,能够与西方的哲学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但同时它拥有它自身的特点,真正形成属于中国当代自身的系统,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才会有主心骨,才会具有一个创造性的本源,才能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最后,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形上学,是一种哲学,其所关注的核心在教化。这种儒学“教化”的哲学意义,要在人的实存及其内在精神生活转变升华的前提下实现生命的真智慧和存在的真实,以达于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之境;由此,人对真实、真理、本体的认识,亦被理解为一种经由人的情感、精神、实存之转变的功夫历程,而为人心所呈现并真实拥有,而非一种单纯理论性的认知。这使之能够密切关联于社会生活,表现为一个内外统合的生命整体。这就要求学者在经典方面的传习讲论中同时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构成当下的思想世界;而经典的学术研究也在这种不断当下化了的思想视域中,参与着思想的生产。因此,它也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哲学学院化之可能性与努力之方向,即要建构以教化为职能的儒家当代思想形态。过去儒学长期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工作,与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应该注意到民间社会学术形态与社会生活样式的重建,培养学者成为有教养的“中国人”,成为以身体道者。只有儒学当代思想实现了双向建构,即理论和社会生活、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起来,其整体乃能逐渐影响到新的当代思想形态之建立。(本文基于我参加一次学术论坛之讲稿。我近患眼疾,读写不便。本文由我口述,博士生王宇丰录音记录整理补充成文。学生田智忠、许家星也参加了本文的相关讨论。)
仁的“偏言”与“专言”
——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
向世陵
从“偏言”与“专言”的角度解说仁,起初是程颐仁说中一个比较专门的话题,即由他之解《周易》而来的“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1]。程颐之论“仁”,自然是其理论本身的需要,但其渊源,却始自先秦以来儒家对于“仁”这一概念的不同界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仁义礼智诸德关系的认识。鉴于“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理学家对此发生兴趣就是理所当然的。其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
一
《周易·乾卦·彖辞》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等语,这是程颐言仁之“偏言”与“专言”说的源头。在语词上,“乾元”之称,显系将卦名“乾”与卦辞“元亨利贞”之“元”整合起来的结果。《彖辞》称颂乾元伟大,突出的是乾的创始作用,天地万物均凭借乾元而生起。
唐代孔颖达引《子夏传》的始、通、和、正为元亨利贞“正义”,并将其概括为四德。所谓“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2]。德者,得也,乾卦凭借其阳性、阳气的创生作用,使所生的万物秉性和谐并得到了最符合它们自身需要的利益和效果。从而,性气合一的生生流行就是乾卦四德的实质,这也是天地间最大的善。圣人则当效法乾元生生而推行此善道。
不过,就《彖辞》自身而言,却既未言善也不及仁,立足善与仁解四德,是《文言》进行再加工的结果。后者曰: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四德之间,元之长善,实质在长人,而人者仁也,所以善之长便归结到君子的以仁为体和仁爱的普施;其余三德,亨通而合乎礼,必然会有众美之嘉会;物各得其利而不害,体现的乃是义之和谐;而固守正道,则足以成为事之主干。那么,天德一方的元亨利贞,已经演绎成为人世的人伦道德体系,四德由天道进入到了人道。参照孔颖达的疏解,四德又与春夏秋冬相配,体现的是一年四季生长收藏的气化运行。从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3]。人世间的德行均因法天而来。君子仁道充实又博爱众生,所以能成为人之尊长。就是说,“泛爱施生”的普遍关爱作为善或仁德,正是君子效法上天“元”德的结果。
在孔颖达看来,天道的四德流贯于人世实际就是仁义礼智,但《文言》本身只言及仁义礼而并未及智,这如何能与人世之四德相通呢?而且,如果不是死咬文字的话,孟子当年强调的仁义礼智之性已经可说是人世之四德,并有“四端”与之相呼应。所以孔颖达也需要予以衔接过渡。他的解释是“(元亨利贞)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智者,行此四事,并须资于知”[4]。就是说,就元亨利贞落实于政事言,表现为仁义礼信,智在这里不是缺失,而是所有这“四事”的施行,都不能离开智慧的运用。所以,智虽未言,却早已融入仁义礼信之中。
孔颖达之解,显然是以五常来回应四德。事实上,在儒家学者那里,五常与四德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各自对应的天道和解释的侧重有所不同,即相对于木火土金水五行,言仁义礼智信五常;相对于春夏秋冬四时,则言仁义礼智四德。所以,孔颖达能方便地将智加入其中,这就为后人直接以仁义礼智诠释四德做好了基本的铺垫。
二
程颐对元亨利贞四德的解释,自然要借鉴汉唐人士的智慧,因而注意四德与五常的关联。对于其间的关系,他的看法是:
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须要分别出。若仁则固一,一所以为仁。恻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一作便有)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若以东为西,以南为北,则是有不信。如东即东,西即西,则无(一有不字)信。[5]
程颐把四德五常都收归到性上去说。从性上言“五事”,必然会涉及仁的统一与五常之“分别”以及仁性与爱情等方面的关系,还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信”的问题。在这里,仁作为“一”,实际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仁本身就是四德或五常之一,作为内在之性,发于外便表现为恻隐之心;二是仁又是一个融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整体性概念,能够以一统四,正是仁所具有的品格。至于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意味凡事出以公心,人我一致而无偏爱。但恕道虽说是入仁之门,又毕竟不等于仁本身。问题到最后,其实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之性与表现于外的“四端”即恻隐等情感的关系问题。四端所以未涉及信,在于它不是必要,因为信是相对不信而言,也不存在信的情感或发端的问题。
程子又说: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礼者别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万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恻隐之类,皆情也,凡动者谓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后见,故四端不言信。)[6]
以“公”解仁,突出了爱人的公平无私和普遍性的品格;义礼智则在表明对对象的把握和处置恰到好处;信却有不同,它只是在确认五常之性的存在。可以说,凡物皆有性,性静而情动,恻隐等等便属于性之发动的情感。同时,性本于天而与人的生命同在,这直接就意味着信(性在人的成立),故不需另言。只有在天性被障蔽即“不信”的时候才会出现信的问题。那么,在程颐看来,五性之中是“仁义礼智”四德必有而“信”可缺,这既可以说是重视信——四德五常都必须是实存而不可少;但也表明,理学家的心性(性情)理论建构,可以不需要信的范畴而建立。当然,这并不会危及信作为五常之一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程颐虽也不少论及五常,但往往是作为过渡,重点已转向对仁之义及与其他诸德关系的考虑。他说: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乾健坤顺之类,亦不曾果然体认得。)[7]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说明程颐根本否定了汉唐诸儒对“仁”之义的解释。仁作为儒学的核心范畴,在程颐之前已有多方面的揭示,譬如恻隐、孝悌、博爱、公正,等等。但是,程颐以为它们都有不完全的缺憾。关键的问题,是要能从“仁之道”中分别出五常来。如果只是讲仁的“兼体”,仁就只能是与诸德相互平行的概念,而否定了其包容和统属的功能。在程颐看来,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如同人的头脑与四肢的关系一样,其主从位置是不应当混淆的。《文言》讲“元者善之长”,并不意味着“元”作为众善之首只是位序的优先,即与随后的亨利贞是并列的概念,而是强调仁具有统属四德的性质,它作为“善之长”而顺序演绎成四德,仁德生生而有全体。故通过八卦来揭示的《易》之大义,就是通过乾元来彰显的生生之仁。圣人则因其“体法于乾之仁”而能“长人”,而“体仁,体元也”[8]《文言》的体仁,归结到圣人(君长)效法于乾元而长人上。
从卦象上说,乾为天,但天又有“专言”与“分言”之别:“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9]就此来看,“天”之一词,如果分从形体、主宰、功用、妙用或性情的不同方面言,可以用天、帝、鬼神、神、乾的不同概念去表述;但若专就“天”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道。“专”之字,在程颐那里有专门、专一、专擅等内涵,“专言”即意味专门集中言,并带有整体而非部分的意义:“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10]与之对应的“分言”,自然是分别就“天”的一个方面特征而言之,这可以从生生流行与横向展开的不同角度去进行揭示。比方,“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11]四德之义的广大,由乾元的“善大”步步引出,“善之长”是仁德,也是贯通四德的最重要的性质。
因而,程颐又说:
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12]乾元的伟大,就在于其所贡献的创始万物之道。四德、五常的意义也都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程颐以五常之仁解说四德之元,立足点可以说是仁的生意。“偏言”就是“分言”,即只就每一德或每一常自身而论,着重在这“一事”自身的性质、表现及特征等等;“专言”在此则不仅有专门集中言之义,更是突出了包容统属的功能。因为不论四德的亨利贞还是五常的义礼智信,都来源于乾元或仁的生气流淌,它们作为不同的德目,各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特色,但终究又依赖并被包含在元或仁的善之统体之中。从而,天地万物、人伦五常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既有主从之分又相互发明、既有整体一贯又有各自特色而不能互相代替的结构。
程颐提出仁义礼智的“偏言”与“专言”说,中心都是围绕仁说话,因为仁事实上具有不同的性能,不可能以一个标准来限定。孟子当年讲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等“四心”而表现为人的不同道德情感及意志行为。这里虽然突出了四德的区分,但它们四者毕竟又构成一个同“根于心”的德性整体,故其区分与总成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孟子终究没有合性理与生理为一的仁的概念,仁主要作为德性、情感存在而非生生之源,所以四德虽是内在的却不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后来韩愈讲仁、义、道、德的顺序递进,仁义已随道德主体的践行而有逻辑地展开,相互间已具有一种有机的关联。[13]到程氏兄弟,随着对《易》之“生意”和“生之谓性”等命题的重新审视和吸纳,生意的流淌已成为他们仁学理论建构必不可少的内在黏合剂。比方程颢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4]
将韩愈的道德仁义代入,“生”所以能作为天地之大德,就在于它在根本上促成了仁之善德源源不绝地生长,并通过天地气运交感而凝聚成各自形体性命的过程,使普遍之善凝聚为个体之性(善)。在此人与天地“一物”的意义上,人之爱人,其实就是人物同一的普遍仁性付诸实现,而不应当自我局狭。人既有禀赋了此必然的生意,恻隐之心的生发就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程颐同样以“生道”定义仁心的发端,认为“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15]。而且,“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6]。恻隐之心的触发,正赖于由生意而来的仁性的发动;而一当仁性发动,乾元生,义礼智诸德遂会因时因地而生成。此一机制颇受朱熹推崇,他称赞道:“程子‘谷种’之喻甚善。若有这种种在这里,何患生理不存!”[17]随此生意而下,“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18]。当然,程颐本人并未有朱熹这样的明确论述,但从其乾元始万物的道理和“体仁,体元也”[19]的原则来说,因生意而有四德的有机整体,也是符合程颐思想的逻辑的。
三
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涵摄宇宙论的生理,重在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已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但是,作为话题的提出者,程颐自己对区分仁之“偏言”与“专言”毕竟没有做出更多的发明,而且本身也存在灵活解释的问题。他留给后来的学者及其仁说理论的,更主要的是一个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或标准。朱熹在与其弟子的交流中对此便多有讨论。例如:
(朱熹)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以气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仁则为慈爱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逊;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问:“如何不道‘鲜矣义礼智’,只道‘鲜矣仁’?”曰:“程先生《易传》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专言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义也在里面;‘知觉谓之仁’,便智也在里面。如‘孝弟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爱而言。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才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20]
春夏秋冬、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可以解释为天(乾元)之生物的过程。“坯朴里便有这底”,说明仁性内在,随其生发和流行于人世,表现为真实可信的四德五常及其慈爱、刚断、谦逊、明辨诸情感品行。但学生的问题也由此开始。即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不说“鲜于义礼智”,这当作何理解?朱熹于是以程颐论“专言”和“偏言”作为鉴别标准去规范孔门的论仁诸说,他为此举过不少例证,就此段论述而言,“孝弟为仁之本”“巧言令色鲜矣仁”“泛爱众而亲仁”等被划归偏言;而“仁者必有勇”“知觉谓之仁”“克己复礼为仁”等则成为专言。
具体来说,一方面,“孝弟为仁之本”“泛爱众而亲仁”之间尽管也有孝亲与泛爱众的差别,但总体都是围绕爱人发论,并不涉及仁与其他德行的关联,故朱熹归之于偏言;而学生发问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言下之意是“鲜矣”也应当包含义礼智在内——这实际上是将仁视作专言。朱熹对此没有直接回答,他在《集注》中曾引程子的“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说明,巧言令色“绝无”仁,或曰仁者绝不会巧言令色。[21]而在此处,由于只是针对“巧言令色”者绝非真心爱人这一事,尚未涉及刚断、谦逊、明辨等其余德行的问题,仁在此与义礼智之间便是并列而非包容的关系,故仍归于偏言。另一方面,智、仁、勇本为一体,《中庸》称“所以行之者一也”,即言一已含三,故归于专言;至于“克己复礼为仁”,由于在克己去私或曰“为公”的氛围下,内在之仁昭显,义礼智本来已融于这一工夫之中,四德贯通为一个整体,故当属于专言的范畴。
不过,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专言”问题,常常又是将其纳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2]的框架中去处理的,体现出他对这一问题更多的思考。如说:“‘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23]如此的分合,可以放在他的理一分殊格局来看,即凡有一物便有一物之理,理虽不可见,但从发于外的爱、宜、恭敬辞逊、分辨是非的行为,可推知它们各自都源于其内涵之理;而所有分殊之理又统一到仁这一总理即心之德中,此种仁包四德的心之德,就是朱熹的“保合太和”[24]。那么,如此的分合就不只是概念的辩解,在现实中,由于仁作为“生理”而发生作用,它实际表现为一体连续的过程。如:
先生曰:“某寻常与朋友说,仁为孝弟之本,义礼智亦然。义只是知事亲如此孝,事长如此弟,礼亦是有事亲事长之礼,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为心之德,则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专言则包四者’是也;‘爱之理’,如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动处便见。有感而动时,皆自仁中发出来。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圆池,池虽不同,皆由水而为之也。”[25]
孝悌是根基性的道德践履,但它之生成又依赖于内在的仁性,并表现为对父母兄弟的亲爱之情;相应地,义礼智分别体现在践行孝悌的适宜恰当、礼仪周全及对孝悌之道的认知把握上。就此分别地看待仁义礼智各自的特性和表现说,都可归于偏言;但是,四德又都依存于心并统一于孝悌的行为,再由孝悌(亲亲)推广到仁民、爱物,使仁的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就后者论,仁作为心之德,已将义礼智包容在内,随事有感而发。不论仁的发作流动怎样表现,如水流成池而有大小方圆,但总之都是同一水所造成,事实上是同一个仁,所以谓之专言。那么,偏言与专言在朱熹又是可以相互过渡的。
因此,偏言和专言,实际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譬如朱熹对“小仁”和“大仁”的分析:“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26“小仁”与“大仁”的比喻不是不可以,因为这有助于认识清楚各自的定位和内涵,但又不能以僵化的态度去截然对待。在根本上,仁只有一个,偏言与专言是从不同层面对仁之意蕴的阐发。所以,对于仁的“偏言”与“专言”问题,“看得界限分明”只是问题的一面,更要注意到双方的相互包容:“说着偏言底,专言底便在里面;说专言底,则偏言底便在里面。”27]如在孟子,说“仁,人心也”是谓专言之仁,因为义礼智本是仁心发散的产物;但同时孟子又言“仁之实,事亲是也”,是特指孝亲这一事,仁又成了偏言。所以“专言”与“偏言”都是“相关说”的。[28]
“相关说”者关联孔子论仁的不同解答,但还有一种情况,即同一句话既可以是偏言又能够做专言,例如前面提及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是归于偏言;但他又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如从心之德的视域去看[29],又可以归于专言。之所以如此,基本点仍在于生气流行,“心之德”便可以是“爱之理”也。朱熹解答说:
“‘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气上看。如春夏秋冬,须看他四时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凉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气之长,秋是生气之敛,冬是生气之藏。若春无生物之意,后面三时都无了。此仁所以包得义礼智也,明道所以言‘义礼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抚使,更无一个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抚也。今学者须是先自讲明得一个仁,若理会得后,在心术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见得此仁,则心术上言仁与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30]
“爱之理”与“心之德”的沟通,需要从一气流行又有四时界限上去看。一方面,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各有其性,凉寒热之性本身不能生物,只有温厚的春气,才是天地生物之心的最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春气温厚又不止于一时,它是流动不息的。在充满生物之意的春气熏陶下,夏秋冬的热凉寒之性被化解,热成为生气之长,凉成为生气之敛,寒则成为生气之藏,一切融入整体的生意之中。不论是观念上辨仁,还是实践中施仁,都能够贯通无碍。从此生意看问题,便能够领会程颢之言“义礼智皆仁也”的意义。朱熹举例是福建路安抚使通常由福州知州兼任,两个职位是同一个人任,对这同一人来说,州之专守与路之巡察,即偏言与专言是整合为一体的。
那么,从根本上说,只要生生不息,便仁德常在。“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31]一切都要归到天地生物之心上说,天地人物的情感发用,都是此心的作用和表现。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关键在能否亲切体验。所以一旦能祛除己私,人的居处、执事、事亲、事兄直至恕物的各种活动,都是仁体的流行。所谓“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2]。
因而,不论是仁的“偏言”与“专言”,还是“爱之理”与“心之德”,重点仍在仁的融会贯通。如果真正明白了“仁”之义,则双方的沟通便不是问题。按朱熹《仁说》的归纳: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33]
朱熹的仁说从《易传》走过来,强调“君子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34]。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元亨利贞,由于仁之生意的不可断绝,仁义礼智四德的一以贯之就是必然的。分别从体用关系说,在体一方,仁包仁义礼智而构成为整体的德性;在用一方,爱恭宜别之情统一于恻隐而无所不贯,相对于“偏言”的特定发明,朱熹可能更看重“专言”的一体流行。不过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熹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四德各自的体用,实际上都可统一到仁德自身的体用关系上。基于生气流行,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学者所以需要在“克己复礼为仁”上做功夫,就在于克尽己私才能使仁性昭显,私欲去而公(天)理显,普天下流行的是同一个温厚生意,无所适而不在。
朱熹对《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
诠释及其意义
乐爱国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此,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并将孔子所言解读为:“只要是主动地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从没有不教诲的。”[1]钱穆《论语新解》说:“束修:一解,修是干脯,十脡为束。古人相见,必执贽为礼,束修乃贽之薄者。又一解,束修谓束带修饰。古人年十五,可自束带修饰以见外傅。又曰:束修,指束身修行言。今从前一解。”[2]显然,钱穆把“束修”解读为“干脯”,类似于杨伯峻。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不同意将“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而是解读为“年十五以上”,并且认为,这种解读与孔子所讲“十有五而志于学”、《书传》“十五入小学”相应。为此,他把孔子所言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3]显然,这一解读,与杨伯峻、钱穆相去甚远。宋代朱熹《论语集注》把“束修”解读为肉脯,但不只是“见面薄礼”,把“束修”诠释为“心”,表达为心意,其中蕴含了许多合理的思想,可以为今人的解读和研究提供启迪。
一、束修:是“礼”还是“十五岁以上”
对于《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西汉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4]孔安国只是讲到“奉礼”而需要“束修”,并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进一步解读。孔安国还在注《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时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伎艺,其心休休焉。”[5]也没有对“束修”是什么做出解读。
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但是其《论语郑氏注》大约于宋初开始失传。近年来,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研究有较大进展。有学者以《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塔那184号墓72TAM184:18/7(b),18/8(b)《论语郑氏注》之《述而》篇第9、10行为底本,并且结合敦煌文献,认为唐写本郑玄注的原文应该是:“自(始)行束修,谓年十五之时(奉?)酒脯。十五已上有恩好者以施遗焉。”[6]“束修”对应的是“酒脯”。郑玄还在讲到亲朋好友结婚、自己有事而无法前往需要遣人送礼时,说:“其礼盖壶酒、束修若犬也。”孔颖达疏曰:“礼物用壶酒及束修。束修,十脡脯也。若无脯,则壶酒及一犬。”[7]显然,在郑玄那里,“束修”是一种与“酒脯”有关的礼物。
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曰:“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应者也。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贽,至也,表已来至也。上则人君用玉,中则卿羔、大夫雁、士雉,下则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其中或束修、壶酒、一犬,悉不得无也。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贽,行束修以上来见谒者,则我未尝不教诲之。故江熙云:‘见其翘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贽见。修,脯也。孔注虽不云修是脯,而意亦不得离脯也。’”[8]显然,皇侃把“束修”解读为“十束脯”,并且还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与“脯”有关。该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孔颖达虽然在《礼记正义》中说“束修,十脡脯也”,但在《尚书正义》中疏孔安国“如有束修一介臣”时,却说:“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节,此亦当然。”[9]他认为,在孔安国那里,“束修”为“束带修节”。
南北朝范晔撰《后汉书》,唐代李贤等为之作注。其中注《伏湛传》“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曰:“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10]又注《延笃传》“且吾自束修以来”,曰:“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1]在这里,李贤既讲“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又讲“束修谓束带修饰”,应当是指年十五以上自行束修,“束带修饰”。因此,“束修”是就“束带修饰”而言,而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可见,汉唐时期诸儒解读“束修”,既有如郑玄解读为与“酒脯”有关的礼物,或皇侃解读为“脯”,也有如李贤解读为“束带修饰”,虽然郑玄、李贤的解读与“年十五以上”有关,但都不是就“年十五以上”而言。
李泽厚《论语今读》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是依据1943年出版的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所言:“《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12]这段言论实际上来自李贤等注《后汉书》。应当说,无论是李贤,还是郑玄,都没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
清代毛奇龄对“束修”多有研究。他的《四书剩言》说:“《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贽见薄物,其见于经传者甚众。如《檀弓》‘束修之问’,《穀梁传》‘束修之肉’,《后汉·第五伦传》‘束修之馈’,则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问之礼为言。若《孔丛子》云‘子思居贫,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为当也’,此犹是偶然馈遗之节。至《北史·儒林传》‘冯伟门徒束修,一毫不受’,则直指教学事矣。又《隋书·刘炫》‘博学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然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则直与《论语》‘未尝无诲’作相反语。又《唐六典》‘国子生初入学,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则分束帛与修为二,然亦是教学贽物。近儒以汉后史书多有‘束修’字作‘约束修饬’解,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荐管宁‘束修其躬’类,遂谓‘束修’不是物,历引诸‘束修’词以为辨。夫天下词字相同者多有,龙星不必是龙,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强同之,谬矣。试诵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将之而上乎?”[13]在毛奇龄看来,《论语》所谓“束修”,一直以来就被解读为“贽见薄物”,是见面的薄物之礼,同时,汉以后所修史书中所谓“束修”,有些并不是指薄物之礼,而是指“约束修饬”。显然,当时就“束修”是“贽见薄物”还是“约束修饬”,有过激烈争论,而毛奇龄赞同把《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中的“束修”解读为“贽见薄物”。
后来的方观旭撰《论语偶记》,根据李贤等注《后汉书》所引郑玄注“束修”而言“谓年十五以上”,说:“盖古人称‘束修’,有指束身修行言者。《列女传》秋胡妇云‘束发修身’,《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修,得宿卫’,《后汉·延笃传》曰‘且吾自束修以来’,马援、杜诗二传又并以束修为年十五,俱是郑注佐证。《书传》云‘十五入小学,殆行束修时矣。'”[14]这里把“束修”又解读为束身修行。
刘宝楠《论语正义》接受毛奇龄的说法,认为《论语》中的“束修”为“贽礼”,即见面礼。他还说:“李贤《后汉·延笃传》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注《论语》曰“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郑注,所以广异义。人年十六为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故举其所行之贽以表其年。”[15]也就是说,郑玄把“束修”说成是“年十五以上”,是指“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刘宝楠还认为,“《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曰‘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皆以‘束修’表年,与郑义同”,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束修”是“以约束修饰为义”。因此,刘宝楠说:“后之儒者,移以解《论语》此文,且举李贤‘束带修饰’之语,以为郑义亦然,是诬郑矣。”[16]他认为,郑玄不可能把《论语》“束修”解读为“束带修饰”。
与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于“束修”的解读不同,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是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郑君注如此,汉时相传之师说也”。黄式三还说:“《后汉·伏湛传》杜诗荐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笃曰:‘吾自束修以来。’注:‘束修,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异于郑君。然《书·秦誓》孔疏引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为某传束修一介臣之证,是孔郑注同。盖年十五以上,束带修饰以就外傅,郑君与孔义可合也。”[17]显然,黄式三是要说明“束修”为“束带修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把“束修”解读为“十五以上可以行贽见师”,还是黄式三《论语后案》把“束修”解读为“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他们都把“束修”看作“礼”,并且与“十五岁以上”有关。但这并不可说明“束修”是就“十五岁以上”而言,不可由此得出“束修”就是指“十五岁以上”。
与此不同,李泽厚《论语今读》根据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黄式三《论语后案》中的有关文献材料,把“束修”解读为“十五岁以上”,实际上是把重点落在年龄上,而不是落在“礼”上,这不仅不同于刘宝楠《论语正义》,而且也不同于黄式三《论语后案》,甚至不同于所有把“束修”看作“礼”的解读。把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解读为“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更像是说孔子在做义务教育。
二、“修,脯也。十脡为束”
继孔安国注《论语》“自行束修以上”之后,皇侃之疏明确讲“束修,十束脯”,“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后来,孔颖达讲“束修,十脡脯也”,北宋邢昺也疏曰:“束修,礼之薄者。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而来学者,则吾未曾不诲焉,皆教诲之也……‘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者,按:《书传》言束修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18]此外,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在论及“束帛、束修之制”时说:“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疋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19]可见,在皇侃讲“束修,十束脯”之后,较多学者认为“束修”为十脡脯,其实只是一束。在数量上有了变化。
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曰:“修,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20显然,朱熹所作的注释,就“束修”而言,与皇侃有一定的相像性。如前所述,在皇侃那里,“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而在朱熹《论语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皇侃讲“束修,十束脯”,朱熹讲“修,脯也。十脡为束”,与孔颖达、邢昺等相同。朱熹还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21]这里所谓“羔雁是较直钱底”,即皇侃所说“中则卿羔、大夫雁”。
其实,朱熹不仅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束修”解读为“修,脯也。十脡为束”,而且还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也同孔颖达《礼记正义》那样讲“束修,十脡脯也”[22]。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在数量上等同于皇侃所谓“束修,十束脯”。
平心而论,朱熹对于《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解读,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过皇侃、孔颖达、邢昺。那么,朱熹的解读,其新意又何在?
以朱熹为首的宋代理学家,其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实际上并不只是停留于字面上,其重点更在于探讨这些字面含义背后的所以然之理,因此,要在弄清楚孔子所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字面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即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朱熹所谓:“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在朱熹看来,之所以要“自行束修以上”,是因为如果没有“束修”,那么就“不知来学”,“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与此相反,“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照朱熹这一解读,孔子之所以要求“自行束修以上”,其目的只是在于表明来学之诚意,并能够据此而有往教之礼;而之所以“未尝无诲”,是因为“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
在《论语》中,孔子讲“仁”,“仁者爱人”;而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则不仅讲“仁”,而且讲“仁者之心”“仁之体”。朱熹注《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23]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指自己欲立达,由此而想到他人也欲立达,这是“以己及人”,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至于仁者为什么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引程颢所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已。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24]也就是说,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朱熹注“束修”所说“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能够“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做到“诲人不倦”。
孔子不仅讲“仁”,而且讲“恕”;而朱熹则不仅讲“以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还讲“推己及人”,并讨论“仁”“恕”之别。朱熹注《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并引述程颢所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25]。认为孔子所谓“恕”,即“推己及人”。据《论语》所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对此,朱熹注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6朱熹认为“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为“仁”,而“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恕”;“仁”为“不待勉强”“自然而然”,“恕”为“推己及人”。
朱熹不仅讲“仁”“恕”之别,而且特别强调“推己及人”为“仁之方”。朱熹《论语集注》在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的同时,又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27]认为“能近取譬”,从自己所欲而推知他人所欲,推己及人,是仁之方。据《论语》所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朱熹注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28]认为孔子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及人”,可以终身行之。这也就是朱熹注《论语》“束修”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因而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也就是说,若能够“自行束修以上”,以礼而来,那么就能知得来学,因而才有“往教之礼”。
三、“束修”之理
孔子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如果把“束修”解读为“干肉”,很容易使今天的人们联想到孔子是把“束修”当作教人的报酬。问题是,孔子肯定不是为了获得“束修”而教人;在一定意义上看,“自行束修以上”只是“礼”,所以孔安国解读为“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汉唐儒家把“束修”解说为或干肉之类的“贽见薄物”,或“束带修饰”,都是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朱熹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29]在朱熹看来,“礼”和“钱”是不能混淆的,而有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才有“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由此亦可推想,李泽厚《论语今读》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并且能够得到一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担心如果把“束修”解读“干肉”,会与教人之报酬混为一谈,而导致所谓“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并与孔子讲“有教无类”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冲突。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束修”,包含了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认为“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但是,在朱熹看来,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不止于“礼”,又超出了“礼”的层面,而是在落实“推己及人”之恕道,也就是说,通过“自行束修以上”便能够知得来学者,而最重要的是知得来学者的诚意,由此才能有往教之礼。
朱熹对于孔子所谓“束修”的解读,重视谢良佐、杨时等人的说法。他的《论孟精义》引谢良佐所说:“束修不必用于见师,古人相见之礼皆然。言及我门者苟以是心至,未尝不教之。”又引杨时所说:“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30]也就说,“束修”不只是“礼”,而是“心”,是来学者的诚意之心。朱熹的理解与此完全一致。为此,朱熹还说:“诸说无他异。”[31]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之后,接着又注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指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32]朱熹还说:“愤悱,便是诚意到;不愤悱,便是诚不到。”[33]在朱熹看来,老师教学生,要根据学生是否有诚意而施教,这与朱熹注“束修”所表达的根据来学者是否有诚意而决定是否行往教之礼,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对于孔子所谓“束修”,既可以从“礼”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礼,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以表达为心意。
同时,由于“束修”的目的在于教学,“束修”之礼和“束修”之理对于教学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束修”之礼,作为“礼”,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外在的。教者为“束修”而教,学者为“束修”而学,“束修”与教学二分,不能真正落实儒家“为仁由己”的“为己之学”。与此不同,“束修”之理,作为“理”,即为心之诚意,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内在的。诚意不仅是教学的内在根本,也是为人之根本,所以,“束修”之理所包含的诚意,与教学互为一体。
因此,朱熹把孔子所谓“束修”解说为“修,脯也。十艇为束”,虽然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朱熹从“理”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理,诠释为“心”,超越了以往只是从“礼”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礼。而且,这种对于“束修”的形而上学的诠释,也是后来学者未能超越的。
四、余论
对于朱熹解读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提出的“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后来的王夫之多有批评。他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己之心而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而安能已于吾心哉!始来学者,执束修以见,则已有志于学,而愿受教于吾矣。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益教者之道固然,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学而上达,存乎其人而已矣。”[34]王夫之认为,教者在于教,而不能不教,这是教者之道,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心”。显然,这是针对朱熹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言。
诚然,就一般道理而言,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二者是一致的。就具体而言,对于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朱熹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王夫之讲“未尝无有以诲之”,二者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对于没有执束修以见,且不知是否来求学者,朱熹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无论是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还是没有执束修以见的非来学者,都必须是“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显然,王夫之对于儒学之道的理解,与朱熹是有一定差异的。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述了历史上各种关于“束修”的解读,也包括清代毛奇龄《四书剩言》、刘宝楠《论语正义》、黄式三《论语后案》的观点,但并没有就“束修”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只是引述《四书诠义》所言:“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而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公之至也。”[35]显然,这一引述大致依据朱熹的解读而来。所谓“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讲孔子无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这与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是一致的;所谓“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正是依据朱熹所言“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朱熹生活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宋代理学追求自我,追求成圣,自我意识日益强大,人们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朱熹重视人与人之间因气禀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尊重他人自己的选择,讲“不知来学,
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这与当时人们强调自我意识,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王夫之所在的明末清初,人们的自我意识日渐弱化,启蒙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夫之强调“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也可见得其合理之处。换言之,儒家在不同文化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体现出内部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儒学来说,其根本宗旨是不变的。先秦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当然,仅仅停留于这些基本原则是不够的。正是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朱熹既讲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又要求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在对孔子所谓“束修”的诠释中,既提出“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的基本原则,又阐发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具体待人之道。相对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朱熹不仅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且还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这不仅在对“束修”的诠释上超越了以往的诠释,而且对于理解儒家的待人之道也颇有新意,同时对于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尊重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相比之下,现代各种解读,大都不是接朱熹而来,也不同于王夫之,而显得较为肤浅。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依据汉唐诸儒的一家之言,把“束修”只是理解为“束修”之礼,不能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为“束修”之理,很容易被误解为孔子教人,需要收礼,需要获得报酬,而不是出于“仁”之理;李泽厚《论语今读》讲“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则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似乎能够克服孔子教人需要收礼、“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误解,体现一种平等的义务教育,但这样的解读,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文本依据。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肖永明
一、问题的提出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携范伯崇、林择之等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九月八日抵达长沙。在长沙停留的近两个月中,朱熹与张栻就《中庸》、“太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与交流。十一月,张栻与朱熹溯湘江而上,同游南岳,随后朱熹返回福建。这次交流与对话,就是反复为后世所传颂的“朱张会讲”。
本来,“朱张会讲”对朱熹、张栻两位学者而言,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当时,朱熹37岁,张栻34岁,两人学术体系都处于正在建构、发展,有待成熟、完善的过程之中,还并不是后人眼中地位崇高的学术大师。从朱熹、张栻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这次会讲的认识和定位也很明确,就是相互切磋、商榷,共同探讨、对话。事实上,当时朱熹和张栻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并无明显差别,同时代很多学者提及这两位学者时,有的先说张栻,后说朱熹,有的先说朱熹,后说张栻,说法并不一致,并没有明显的尊此抑彼的倾向。
但朱子弟子后学为了树立朱子学的权威,强化朱熹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按照朱熹为主导、朱熹地位更高、在会讲过程中张栻更多地接受了朱熹之学的思路对朱熹、张栻的“会讲”加以叙述,在叙述中体现出朱熹、张栻学术地位的高低与社会影响的强弱,这实际上就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一种塑造和建构。随着朱熹地位的不断提高,尤其当朱子学成了学术主流、官方哲学之后,朱子后学的这种塑造和建构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传播,甚至湖湘后学为了突出湖湘之学的正统性、正宗性,表明湖湘之学已经超越了湖湘一隅的地域局限而属于主流学术的一部分,也刻意突出朱熹对张栻之学产生影响的一面,彰显朱熹到访岳麓对湖湘学派发展的意义。这样,另外一面,亦即张栻之学乃至整个湖湘学术在朱熹思想学术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在“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以朱熹为核心、正统、主流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自南宋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精心建构,广为流传,又在历代的流传中不断强化,迄今几乎成为学界共识。[1]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后世居学术界的主流、正统地位并无问题,但这种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南宋乾道三年,即将迈向中年的朱熹,其思想理论建构正在进行,学术体系尚未成熟,其正统、主流的地位还没有确立。从历史角度看,朱子弟子后学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未免有失真之处。
因此,本文试图勾勒出“朱张会讲”的基本事实,同时对历代学者有关“朱张会讲”的叙述加以考察,以此从一个侧面了解按照以朱熹为正统、主流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不断建构的过程。
二、“朱张会讲”中的朱熹、张栻
张栻、朱熹的学术思想都源自二程,真德秀曾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2]这既表明张栻、朱熹的思想同出二程,但也表明经过数代传承之后,他们已处于不同的思想谱系中,朱熹为闽学的传人,而张栻则是湖湘学的传人。作为各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已出现颇多差异。而这种学派上、思想上的差异乃是互相交流吸收、质疑辩论的基础,朱张会讲的必要性即体现在这里。
会讲之前,朱熹、张栻已有过面谈,且多次往来通信,讨论、交流学术问题。朱熹说:“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3]又说:“钦夫尝收安问,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如此。非面未易纠也。”[4]而张栻也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不知何日得遂也。”[5]在与陆九龄谈及朱熹时,张栻很是感慨:“书问往来,终岂若会面之得尽其底里哉!”[61在信件往复过程中,虽然二人都颇有收获,但是也感到,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书信中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讨论,而双方的困惑、分歧,更是需要当面商榷、探讨,由此二人产生了当面讨论、对话交流的强烈愿望。从张栻信中可以看到,他觉得很有必要“会见讲论”,这种想法已经在心中盘桓数年之久。而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也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7]他到湖南,是希望和湖湘学者当面探讨,了解湖湘学者在《中庸》问题上的看法。所以尽管“湖南之行,劝止者多”[8],朱熹还是坚持前往。总之,从缘起来看,会讲是朱熹与张栻几年来共同的愿望,目的在于面对面地、更为深入地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解决理论建构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讲只是他们长时期书信讨论的延续和发展。朱熹不远两千里,从福建来到长沙,既不是挑战者,也不是求教者,朱、张二人是平等的学友关系。
关于朱张会讲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已无法详细考证,从存留不多的文献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他们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庸》之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谈到过,王懋竑《朱子年谱》中也有记载:“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9]从中可看出,朱熹、张栻所讨论的是《中庸》已发未发的问题,而且两人都秉持着自己的思想观点,讨论十分激烈。其次,是关于太极的问题[10]。朱、张分别之时,张栻有诗云:“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全无牛。”[11]朱熹亦有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12]再次,是知行问题,朱熹后来说:“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至,下是终之。故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何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13]
朱熹、张栻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很多共识,彼此都感到有收获。朱熹有不少文字谈到这次会讲:
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14]
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15]
熹自去秋之中去长沙……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16]
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171
朱熹认为张栻“见处卓然”,“议论出人意表”,经过此次会讲,自己的收益很大,内心十分钦佩。
后来张栻英年早逝,朱熹在祭文中说:“我昔求道,未获其友。蔽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厉以死守也。”[18]又说:“嗟唯我之与兄,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返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19]虽然朱熹在祭文中不免有谦虚之意,但是可以看出朱熹是把张栻当作自己“志同而心契”“相与切磋”的学术知己与友人的。
张栻亦将朱熹当成思想上的良友,在谈及朱熹时充满赞赏:“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发也。”[20]又说:“元晦数通书讲论,比旧尤好。《语孟精义》有益学者。”[21]谈到会讲,张栻说:“剧谈无俗调,得句有新功。”[22]对于讲会之益是充分肯定的。
从朱张二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们互相欣赏,志同道合。二人皆对会讲中切磋与进益深感满意,大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这一点,也正说明张栻、朱熹都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守着各自的立场,不存在谁依附谁的关系。他们在思想上的交流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朱张会讲是两位学友在共同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三、同时代学者眼中的朱熹、张栻
在与二人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朱熹、张栻只有学问方向上的差异,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陈亮就曾对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在当时学术上的地位有一个整体的评价,他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亮亦获承教于诸公。”[23在他看来,三人均为“一世学者宗师”,并无高下之别。这一点也为辛弃疾、叶适所认同,辛弃疾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24]叶适则说:“(吕祖谦)与张栻、朱熹同时,学者宗之。”[25]甚至对于叶适来说,朱张也并无特出之处,只是属于他所认可的儒者圈中十多位学者中的两位。[26]周必大也说:“近得敬夫并元晦与子澄书,亦是如此,窃深叹仰。”[27]这表明张栻、朱熹对他本人而言并无分别,因此对二人同表敬佩。陈亮后来又说:“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28陈亮在这里指出,同为“道德性命之学”,张栻、吕祖谦的主张已有被朝廷所接受的倾向,而朱熹的学说之所以能行而不止,则是因其“强立不反”。这种表述实际已经暗示了时人对朱张二人学说的看法,进而我们也就可以窥探出二人当时在学术上的地位。另外,陆九渊也将朱张二人相提并论,他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29]陆氏在此虽然表达了对张栻的认可,但这可能出于张栻与他本人的风格更为接近的考虑,而且他对朱熹又抱有偏见。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在他看来,二人的地位并无明显差异。不难看出,在与朱、张同时代的人看来,无论是就学术地位还是就学问而言,二人并无高低之分。
不仅同时代的学者有这种看法,稍后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陈亮、辛弃疾、叶适认为朱熹、张栻、吕祖谦是当时天下学者师表,楼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30与之类似,赵善下则指出三人同处于“鼎峙相望”的地位,他说:“圣学之传,惟曾与轲……千载而下,独我伊、洛……其徒丧沦,寂寥靡传。南轩俶悯,裒然为倡。东莱晦庵,鼎峙相望。惟三先生,相与磋切。扶偏黜异,表里洞彻。”[31]更进一步说,三人能够同为时人所认可,就在于其学问能“自为一家”,正如周密所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32]关于如何“自为一家”,即其各自的特色如何,这一点韩淲曾有过论述,他说:“张敬夫卓然有高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盖张之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33]正是因为三人在学术造诣上各有其特殊之处,故而能为时人所认可。
当时学者还建构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将朱熹、张栻、吕祖谦一起纳入其中。李心传说:“中立传郡人罗仲素,仲素传郡人李愿中,愿中传新安朱元晦。康侯传其子仁仲,仁仲传广汉张敬夫。乾道、淳熙间,二人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伯恭,其同志也。”[34]这种道的传承,丁端祖也有论述:“本朝濂溪二程,倡义理之学,续孔孟之传,而天下学者,始知所适从……又得晦庵朱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复阐‘六经’之旨,续濂溪二程之传,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体,天下均所宗师。”[35]“自濂溪、明道、伊川义理之学为诸儒倡……其后又得南轩张氏、晦庵朱氏、东莱吕氏续濂溪、明道、伊川几绝之绪而振起之,六经之道晦而复明。”[36]方大琮的说法也很相似:“元公在当时号善谈名理……赖二程子阐明之而益大,朱、张、吕扶翊之而益尊。”[37]在他们看来,朱熹、张栻、吕祖谦阐明“六经”之旨,接续周程之道的统绪,都是孔孟、周程之道的传人。
与这一论述稍有差异,也有学者仅将朱、张二人看作是二程道学的传承者,如家铉翁就说:“朱张二先生倡道东南,共扶千载之坠绪,志同而道合,相得而弥章者也。”[38]这一论述,强调朱、张在道统传承之中的作用,却没有提及吕祖谦。尽管如此,以上种种叙述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或朱熹、张栻二人作为周程之道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当一种固定的谱系还未成形,权力还未浸入话语中时,人们表述思想的方式,叙述历史的语言也会相对自由和个性化。虽然南宋士人提及朱熹、张栻、吕祖谦时,多以“朱张”或“朱张吕”来并称,但是其中也不乏“张朱”“张朱吕”的提法。如刘宰说:“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怅怅然无所归。”[39]吕中说:“岳麓、白鹿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回视州县之学,不过世俗之文进取之策,其相去岂直千百驿而已哉?”[40]魏了翁也说:“张、朱、吕诸先生之亡,学者无所依归,诚哉是言。”[41]又说:“二程先生者出始发明本学于道丧千载之余……近世胡、张、朱、吕氏继之,而圣贤之心昭昭然揭日月于天下。”[42]真德秀甚至明确指出“惟时湖湘渊源最正”,在叙述圣人之道的传承时屡次先言张而后言朱:“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濂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43]
在这里,他们的论述都将张栻排在朱熹的前面,称“张朱”。但结合当时学者的整体情况看,“朱张”或“张朱”的提法都很常见。在南宋时期的众多的学者、士人看来,朱熹、张栻,或者再加上吕祖谦,都是孔孟之道、周程之学的接续者、继承人。“朱张”或“张朱”的提法并无区分高下的用意。也就是说,朱、张同为当时的学人所并重,并不存在主次高下之分。
四、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
朱熹在其理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提出了道统说,建构了“圣人之道”的传承谱系,他本人也具有自任的意识。南宋后期,众多朱子后学尊崇朱熹,突出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正宗地位。如黄榦就不遗余力地塑造朱熹的道统接续者形象。他说:“吾道不明且数千年,程张始阐其端,晦庵先生为之大振厥绪。”[44]“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45]在他看来,自周以来,圣贤之道一脉相承,孔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传,而在当世,又只有朱子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陈埴也说:“晦翁出于诸老先生之后,有集大成之义,故程子有未尽处至晦翁而始成。”[46]作为朱学三传的熊禾亦说:“道丧千载,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而后此道始大明于世。”[47]有的朱子后学甚至将这种道统意识编入启蒙读物。如《性理字训》说:“五帝三王,继天立极,道传大统,时臻盛治……惟周与程,统接孟子,继以朱子,疏源濬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瞆,宁不率从?”[48]在他们看来,千年以来圣贤之道不传,到宋代才大明于世,而朱子是集大成者。这些说法,大大突出了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道统谱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儒学的核心和精髓,确立儒学传承的正统和主流,从而排斥其他的学派。朱子后学构建的道统谱系,排他性也是很明显的。在他们的道统谱系中,其他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被排斥在外,只有朱熹才是唯一的正统,其他儒家学者都只是支流余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原本同时代学者们关于朱、张并立或朱、张、吕鼎立的说法被修正,朱、张乾道三年的岳麓会讲也有了另外的叙述。
朱熹高弟陈淳谈到“朱张会讲”时说:
至如乾道庚寅中,南轩以道学名德守是邦,而东莱为郡文学,是时南轩之学已远造矣,思昔犹专门固滞,及晦翁痛与反覆辨论,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49]
如湖湘之学亦自濂洛而来,只初间论性无善恶,有专门之固,及文公为之反覆辨论,南轩幡然从之。徙义之果,克己之严,虽其早世,不及大成,而所归亦已就平实,有功于吾道之羽翼。[50]
在陈淳的叙述中,张栻本来“专门固滞”,在会讲中,朱熹“痛与反覆辨论”,终于使得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按照这一叙述,朱熹在会讲中是传道者,是正统和主流的代表。他对张栻施加影响,使张栻弃其“专门固滞”之病,归于正学。而张栻则是被动接受正统思想影响,最后一改旧说,完全接受了朱熹的观点。因此,虽然张栻英年早逝,“不及大成”,但仍然可以作为“吾道之羽翼”。当然,只是“羽翼”而并非吾道之正传,这和朱熹道统传承者的地位是有着根本差别的。
显然,这一叙述与真德秀关于“会讲”的叙述“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51]有了根本的差异。它大大抬高了朱熹在会讲中的地位,把一场学友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变成了代表学术主流和正宗的朱子对处于非主流、非正宗地位的张栻的说服和收编,把会讲的过程中朱、张立场不同却地位平等的各抒己见、激烈论辩,变成了正宗、主流与非正宗、非主流之间的战胜和抵抗。在这种叙述中,张栻放弃了自己思想的立场,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受其思想的支配。对“朱张会讲”的这种叙述方式,体现了朱子后学的道统观念,成为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不光是朱熹和张栻关系被重新建构,与朱熹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被朱子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重新加以叙述。如朱熹和吕祖谦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吕祖谦了解朱熹之学后,“尽弃其学而学焉”[52]。而与朱熹学术旨趣不同、理论建构路径有异的陆九渊则被叙述为朱熹很想“挽而归之正”,但陆九渊固执己见、偏于一隅。“如陆学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文公向日最欲挽而归之正,而偏执牢不可破,非如南轩之资,纯粹坦易,一变便可至道也。”[53]很显然,陈淳基于道统观念而极力抬高朱熹的这些叙述,完全是出于朱熹正统地位塑造的需要,其核心观念就是,唯有朱熹“渊源纯粹精极,真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当今之世舍先生其谁哉!”[54]
朱门弟子后学对朱子的尊崇与对“会讲”叙述方式的建构大大抬高朱熹的地位,也使得原本与朱熹一同活跃于南宋学术界的其他著名学者黯然失色。在朱子门人后学的不断努力之下,朱子学逐渐被官方接受,朱熹作为孔孟周程的嫡传,在道统谱系中具有了更加牢固的地位。尽管此时的朱子学尚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随着朱子学地位的逐渐上升,朱子后学这种关于朱子地位的叙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栻、吕祖谦等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成为支脉、旁系。朱子门人后学在叙述“朱张会讲”时,也是基于后世对朱、张地位的认识,按照朱子为主、张栻为辅,朱子为道统正宗和学术主流、张栻为支脉和旁系的理解来建构的。在他们看来,说张栻“幡然从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是对张栻的充分肯定,正是张栻的“徙义之果”、最终归于朱熹才保证了他“有功于吾道之羽翼”。
五、元代以后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
元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书目。与此同时,朱熹的道统地位也得到不断巩固,众多儒家学者都把朱熹作为道统传人。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学者在叙述南宋学术史时,就进一步突出了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而将张栻、吕祖谦等仅仅作为朱熹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取资对象。程端礼说:“自朱子集诸儒之成,讲学之方悉有定论。”[55]胡助说:“至宋濂洛诸大儒起,唱鸣道学以续其传。南渡朱张吕三先生继起私淑,其徒相与讲贯,斯道复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诸儒之大成。然后圣人之道昭揭日星,诸子百家之言折中归一。”[56]陈栎亦说:“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又次则东莱……则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南轩固不杂,东莱远不及矣!”[57]梁寅则认为:“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亦皆有志于道,而天不假年,独朱子年弥高而德弥劭,是以挺然为一代之宗师。”[58]可见,到此时,在不少学者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朱熹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儒中第一人,张栻等而次之,吕祖谦再等而次之;张栻纯粹不杂,但不如朱熹,吕祖谦则远不及朱熹;张栻、吕祖谦虽然有志于道,但天不假年,学术成就有限,只有朱子年高德劭,堪称一代宗师。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许多士人的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历史叙事的潜意识。这时,朱熹和张栻已经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等次,因此从文献上看,人们提及朱熹、张栻的时候,大多是称“朱张”,而鲜有人称“张朱”。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吴澄对“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发展史上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59]但是他对朱、张会讲的过程中二人角色有另外一番叙述:“朱子初焉说太极与南轩不同,后过长沙谒南轩,南轩极言其说之未是。初亦未甚契,既而尽从南轩之说。有诗谢南轩曰:我昔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及南轩死,有文祭之曰:始参差以毕序,卒烂熳而同流。是晦庵太极之说尽得之于南轩,其言若合符节。”[60]按照这一叙述,则朱熹太极之说乃“尽从南轩之说”“尽得之于南轩”,这就与朱子门人后学所说的朱熹说服张栻,张栻“幡然从之”的叙述截然相反了。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元代朱熹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朱熹为核心的道统意识渗透到士人的观念之中,但仍有学者试图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不同的立场对“朱张会讲”加以叙述。
到明代,朱熹的集大成地位进一步强化,张拭、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杨廉认为朱熹的集大成在于能将“象山之尊德性,南轩之辨义利,东莱之矫气质固有以兼之……谓之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殆非过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61]章懋甚至以反诘的语气强调张栻、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不能与朱熹相提并论:“南渡之后有朱、张、吕三先生焉……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耶!由是观之,其得斯道之传者,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62]李东阳也认为,张栻之学要逊朱熹一筹:“晦翁之学,因有大于彼(张栻),然亦资而有之……由南轩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吾于吾士大夫望之矣。”[63]
对朱张关系的这一定位,也决定了明清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方式。黄衷在《岳麓书院祠祀记》中谈到“朱张会讲”说:“朱张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之义,尝越三昼夜而不合,然卒定于朱子。”64]在他看来,认为“朱张会讲”定论于朱熹。黄宗羲也认为张栻得到朱熹的帮助之后,方能“裁之归于平正”[65]。清代的杭世骏则说:“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66]他强调的是张栻、吕祖谦“取资”于朱熹,并且把朱子置于当时众多学者学术活动所围绕的核心。
可以看出,明清学者关于朱、张关系和朱、张会讲的叙述,实际上只是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相关话语的延续和进一步确立。张栻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道统叙述的一个配角,一种烘托。“朱张会讲”中,朱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张栻是被说服、被矫正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尊崇朱熹的氛围非常浓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远超南宋诸儒之上的时候,个别学者对朱张关系的定位仍然有与众不同之处,把朱、张一同视为道统正传:“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及出为世用,推之以开物成务、致君泽民,将无不可。”[67]这一说法将朱、张相提并论,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对张栻地位的充分肯定。
还有学者对“朱张会讲”也有不同于“卒定于朱子”的说法,认为二人商讨论辩,虽两心相契,但关于“未发”看法一直有差异:“以此观之,则二先生昭聚讲论而深相契者大略可见,而未发之旨盖终有未合也。”[68]也就是说,“朱张会讲”并非朱熹对张栻观点的覆盖和张栻对朱熹观点的全盘接受,而是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求同存异,有同有异。在当时,能够对“朱张会讲”进行如此清醒理性的叙述,实属不易。
六、余论
“事实”在被“叙述”时,不可避免地会着上叙述者的颜色,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叙述”或多或少会遮蔽掉被叙述者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事实”进行叙述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事实”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建构的方式既受到建构者个人的立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也与时代学术思潮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变化的叙述中便可以得到印证。从最初学者们普遍地认为二人在当时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有的学者看来张栻的地位还要高于朱熹,到后世众多学者认为朱熹的地位高于张栻、在会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化过程,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朱熹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朱张会讲”所呈现的魅力以及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不会这么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在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过程中朱熹与张栻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影响、双方观点各有保留的事实,不能因此将朱熹最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所呈现的形象植入对发生在其早期的“朱张会讲”的叙述之中。本文所关注的是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朱张会讲”究竟事实如何,这一事实又是如何在历代学者不断的叙述中被建构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朱熹审美观探究
尤煌杰
一、前言
从严格意义而言,关于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究,都会有中西学术传统上的差异,进而引发中国是否有“哲学”或“美学”的论战。但是如果我们从各种学术领域当中,得到钻研其研究对象之究极意义的思想理论,就可以说在广义上,中国的诸子百家一系列发展下来的思想就是“中国哲学”。同理,在西洋美学的传统上极注重美的形上学意义,艺术的界定,以及如何产生美感等问题,形成一系列的美学理论。狭义上而言,中国也没有类似西洋美学的理论。但是,中国一样有各种从自身文化发展的艺术表现,论述艺术与道之关系的理论,品味各种知觉活动的审美鉴赏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广义而言,存在中国美学思想。
中西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关于美的课题的理论,大多来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谈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等到艺术家的地位逐渐受到肯定与重视之后,艺术家们的美学思想才慢慢开展出来。所以关于早期思想家们与美学相关的论述,并没有意图在当今我们所理解的系统化美学理论架构下,有意识地、自觉地发展所谓“美学”理论。我们只能说他们对于从感性方面所延伸的课题,结合其哲学思想,予以根源性的说明与论述。这些论述在起初并无意于专论感性问题以形成一特殊理论系统,但是对后世而言,确实为后来的美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建设的基石。例如: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思想,原来的论述要旨在于说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感性活动的论述,却可用来指导后世的艺术创作活动与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使我们现在可以说有某种“儒家美学”或“道家美学”。
朱熹留下许多优美的诗词文章,也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的论述,并有与弟子们互相切磋讨论的对话记录流传后世。在当年应该也没有所谓“美学”学科的概念,但是因为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而延伸出来的论述,使我们可以在广义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来进行关于朱熹的审美观的探究。这是一种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审美观念。这个审美观念透过经典的传递,可以进而实质影响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以及审美对象之鉴赏者的审美观。[1]
本文对于所谓“审美观”的理解,意指通过感性的觉察进而引发某种精神性的观念或情感。所以“感性”活动是审美活动的首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单纯的感觉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审美活动,但是审美活动必要以感觉活动作为起始。对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而言,都需要感觉活动作为起点。认知活动以分析、抽象、推理等理性运作,将“具体”“个别”的感觉内容,抽取出“普遍”“抽象”的概念,因着这些概念而成为传达思想的基本单元。审美活动以直觉或直观的方式处理感觉内容,将这个感觉内容直接联结到某种情感或观念。如果在审美活动中所引发的情感或观念,愈是普及于多数的人使之可以领受到,愈能产生更大的共鸣。
本文期待能通过筛选朱熹有关上述说明之审美活动的言论,加以整理,并尝试理解朱熹哲学理论和审美观之间的理论关系。笔者阐述的方式,将首先检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有关先秦儒家之审美观的批注,再从《朱子语类》中查找朱子与弟子的相关讨论。之后,也寻找朱熹更具个人特色的审美观。
二、朱熹对原始儒家的感性课题的诠释与讨论
儒家哲学对于感官知觉的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此知觉活动的实在性以及此种活动为后续的理性活动提供的一个思想基础,对于知觉活动所提供的内容并不怀疑。
1.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朱熹注:
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观,比视为详矣。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察,则又加详矣。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焉,于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2]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所以,只是个大概。所由,便看他所从之道,如为义,为利。又也看他所由处有是有非。至所安处,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须着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个道理。[3]《论语·为政篇》“观其所以章”本旨是讨论伦理行为的考察与目的,但是
其阶段历程,就其感性活动面而言,亦有可以扩及一般非伦理行为的描述。首先在孔子的言论中,把“视”“观”“察”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与视觉有关的活动。朱熹批注:“观,比视为详矣……察,则又加详矣。”从视觉活动来说,后者比前者增加了更多有意识的聚焦活动,只是在伦理行为的观察上,其聚焦的对象分别是“所以”“所由”“所安”。所“以”是外在可见的“行为表现”;所“由”是“发动行为的内在意念或动机”;所“安”是“享受行为所带来的效果”。在孔子与朱子的原始文脉中,明显地在讨论伦理行为的历程与效果。“视”“观”“察”是源自“主体”有意识的知觉活动,而且有逐级提升加密的意涵。“所以”“所由”“所安”是被观察的“行为者”(作为“客体”)产生的外显行为、行为动机、行为效果。
与视觉有关的词汇,除了以上“视”“观”“察”三个动词之外,朱熹也提及“看”“见”。他说:“阴阳五行之理,须常常看得在目前,则自然牢固矣。”[41
又: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他自见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处,此是可乐天理。[5]上引的“看”或“看见”不是指光学原理上的看见,而是事理上的或人生
境界上的看见,亦即是一种“理会”或“意会”。这些与视觉经验有关的词汇,都不是单指生理性的视觉,而是会加上有意识的或具有“意向性”的观看。在以上的引文中虽然多以伦理行为作为讨论的事例,但是其分析的层次仍然可以运用于美感经验的描述中,只是把观看的对象从伦理行为转换为鉴赏对象即可达成。朱熹从经验上的看见“良辰美景”“日用之间”,向上提升到天理遍在四方流行。因此,由单纯的感性经验上的觉知,变成“可乐天理”。这说明从具象的感性经验提升到对遍在流行的大道的直观,会产生精神愉悦。
2.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朱熹注: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6]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石丈问:“齐何以有韶?”曰:“人说公子完带来,亦有甚据?”淳问:“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今‘添学之’二字,则此意便无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证。曰:“不要理会‘三月’字。须看韶是甚么音调,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闻之便恁地。须就舜之德、孔子之心处看。”[7]
“‘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说得泊然处,便有些庄老。某谓正好看圣人忘肉味处,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又举《史记》载孔子至齐,促从者行,曰:“韶乐作。”从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见童子视端而行直。”“虽是说得异,亦容有此理。”[8]
按照朱熹的意见,他首先根据《史记》增补“学之”二字,使一般人断句的“三月不知肉味”,成为“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又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其次,强调“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据此教人“不要理会‘三月’字”,并否定“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的负面看法。
关于“三月不知肉味”或“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两种句读,孰是孰非,其实各有其理由。一般句读的“三月”不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应是表示很长时间的夸示法。而“学之‘三月'”,就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但是除了《史记》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佐证。所以,朱熹下断语“不要理会‘三月’字”,因为“三月”是否为实指名词都对于本章之解释无关宏旨。
本章的主旨在于记载孔子听《韶乐》的审美经验导致“不知肉味”。这一描述对比了“听”韶乐与“知”肉味,两种不同的知觉经验导致在美感层次上的差异。这个例子肯定抽象的、具空间距离的听觉,压倒具体的、直接的官能接触的味觉。朱熹的解释是“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用现代美学的语汇来转述就是在鉴赏一首作品时,必须有“主体”的鉴赏能力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客体”也必须内含相应的质量,在“主客合一”的状态下完成这个美妙的审美鉴赏活动。
附带一提,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从这一段文献,可以分辨出认知历程与审美历程的差异与交互作用。这段记载所显示的是一种推理过程,说明孔子从“一个特定的行为”,推理出“一个作品正在演奏”。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省略推理。但是这两者之间产生关联性的“联结”,即被省略的前提,却是一种源自美感经验的效果。在文字的背后,没有提及的是“韶乐演奏使人视端而行直”。这个推理严格而言,不是正确的有效推理,但是从孔子当时的有限、特殊情境,可以理解其特定的结论。
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朱熹注:
夫,音扶。舍,上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愚按: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91]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体而言。如“‘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人杰问:“‘乐’字之义,释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某谓:“如仲尼之称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旧看伊川说‘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会未透。自今观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泛滥。且理会乐水乐山,直看得意思穷尽,然后四旁莫不贯通。苟先及四旁,却终至于与本说都理会不得也。”[10]
本节引述《论语·子罕》《子在川上》章,但是关于《朱子语类》则引述《论语·雍也》《知者乐水》章,因为后者的讨论更加简洁与周全。宋儒大致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之叹是对于“道体”之伟大的赞叹,而非议汉儒把它解释为“伤逝”(例如郑玄、何晏、邢昺等人的批注被归类为“伤逝”型)。根据朱熹的批注,具体的“水”的千变万化正是抽象的“道体”的具象表现。再回到鉴赏的主体来看,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能拘泥“知者”与“仁者”的根本差异,或“山”与“水”的本质差异。“知者”与“仁者”就如同“水”的激荡或平静,都是水的同体与不同样态。而“山”与“水”在中国的山水观中也是互相包容与互相依赖,以共成“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景观,即是“山以水为血脉……山得水而活……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郭熙,《林泉高致》)。
本章文献彰显具象观察活动,可以引发超越境界的体验。这种历程不只在纯粹学问性的追索历程上显现,而展示出一种超越直观的境界,也可以解释从具象观察一个审美对象而直观天理大道。说明了思辨活动与审美活动,虽然起点与历程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一同指向永恒大道。
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朱熹注: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11]
《朱子语类》的讨论:问“善者美之实”。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与武王仗大义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争多。只是德处,武王便不同。”曰:“‘未尽善’,亦是征伐处未满意否?”曰:“善只说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处看否?”曰:“是。”谢教,曰:“毕竟揖逊与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个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专就此说。”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毕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诵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见矣。乐便是圣人影子,这处‘未尽善’,便是那里有未满处。”[12]
孔子极度称美于韶乐,认为它同时满足了“美”“善”的极致标准,但是对于武乐则只认为它是具有充分“美”的条件,而缺乏“尽善”的条件。在朱熹的诠释上,认为武王的事功不下于舜,但是在为“德”方面,武王是有“未尽善”的。而此“未尽善”不是武王所愿意或故意的,而是就当时的时局有所“不得已”处。这个解释澄清武乐的“未尽善”不是源自武王的征伐行动的动机不善,而是就其行动本身以及反映在音乐上的属性有“未满处”。这个事例说明对于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美”“善”不是等同的,两者可以兼容,也可以分离存在。但是,以儒家的审美标准而言,一件作品必须以“尽善尽美”作为最终极的目标。
三、朱熹在审美上的发展
(一)感官经验的扩增
儒家审美思想对于感性的肯定是确实的,并且重视视觉经验与听觉经验。在许多讨论中多有触及视、听两种经验。《论语·为政》《视其所以》章把视觉经验更加细致地区分为不同的等级,《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章又把听觉的经验压倒味觉的经验。儒家对于味觉在审美上的地位未给予充分的讨论,但是《老子》的思想却是首开先例对其予以肯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第12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35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63章)。《老子》从否定面来看待“无味”之味,扩张了味觉的意涵,延伸它的应用于抽象观念。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论及“味”字共有320段落,对关于“味”的使用有如下各种组合词汇:滋味、玩味、咀味、意味、涵味、无味、知味、熟味、美味、涵泳讽味、余味、忘味、别味、奇羞异味、气味、声色臭味、味别地脉、辨味点茶、味道之腴、诵味、详味、亲切有味、五味、从容涵泳之味、真味。
这些词汇多半出现在讨论读书功夫方面,把有关味觉的词汇使用在知识之追求,我们不能说这些词汇只适用于知识追求,而是应该反过来思考,朱熹大量借用味觉上的动词、名词、形容词来说明如何在读书功夫上精进。而这些味觉上的词汇应该都是源自审美经验的。这种借用的目的最主要在于体验,而不是词类批注。举例来说:
或问:“孟子说‘仁’字,义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晓说,是如何?”曰:“孔子未尝不说,只是公自不会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说糖味甜耳。孔子虽不如此说,却只将那糖与人吃。人若肯吃,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13]
朱熹诠释孔子的教导方式,举例,若要人认识糖的甜味,那就直接给那人吃糖便知道了。这是一种直接体证的方式,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必然经历的方式。
(二)审美范畴的新解
关于审美经验,我们在本文前言就已提及审美经验不只是感觉经验,必须是经过专注、提炼的经验才能成为审美经验。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一则讨论: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只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
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如此,则世间伊尹甚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14]
以上引文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在这个文脉中“目视耳听”之为“物”,因为它们都是个别的知觉经验,未经有意识的筛选,所以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能够把视听的能力发挥到它这个官能的理想境界,或优越境地,也就是耳聪目明,能在知觉中得出一个值得“玩味”“涵泳”的形式,那才符合“则”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朱熹的思想中隐含着审美经验必须从一般感觉经验加以提炼才可获得的原则。
在朱熹的审美思想中,仍然以儒家美学观为主轴而有别于道家美学观,从《朱子语类》有关《邵子之书》可以看出一些分辨。
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人杰因问:“《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犹未离乎害也’。上四句自说得好,却云‘未离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圣人之中道;‘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说前四句。”曰:“性只是仁义礼智,乃是道也。心则统乎性,身则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于物,则身之所资以为用者也。”曰:“此非康节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议论它?”人杰因请教。先生曰:“‘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又问:“如此,则‘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三句,义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耳。”曰:“若论‘万物皆备于我’,则以‘身观物’,亦何不可之有?”[15]
从邵康节的《击壤集序》先提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四句,又提出“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在整个讨论中,前四句被认为可以用儒家观念说得通,符合儒家的基本观念。但是后来修订的七句,被认为倾向道家,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观念。笔者认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从最大的范畴逐层含摄较小范畴,这个“观”的功能就在于连接上层观念与下层观念的隶属关系。这个连接为进德修业、修身养性,产生一种逐层进阶的提升,有助于伦理教化之功,也符合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是“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它不再在乎上下层次的含摄关系。
邵雍之所以舍弃纯粹儒家的思路,在于他点出这层层约制关系中有“未离乎害”,亦即在含摄过程中有所保留与舍弃,而不能保全整体。而“以道观道……”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套套逻辑论式,而是就“道”自身的本质而考究其作为“道”的展现,以下类推。所以他说:“虽欲相伤,其可得乎?”如此,得以保全各实体的整全面貌。
犹如《易·乾卦·彖传》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道是道,性是性,心是心,等等,从一个万事万物作为存有者的角度,各自保有其本质的特征。就如同《朱子语类》中对于“各正性命”的讨论:
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圣人于乾卦发此两句,最好。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都是正个性命。保合得个和气性命,便是当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个皮壳包裹在里。如人以刀破其腹,此个物事便散,却便死。”[16]
到那万物各得其所时,便是物物如此。“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变化是个浑全底。”[17]
因此,再回到邵康节所称许的“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对照《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两者可以相通,不必然要把邵子的思想立即推向道家那一边去。如此“观”字在此的功能要比前段文字的“以道观性……”的应用范围更广泛,既可以说明形上学的存有状态,也可以作为鉴赏活动或审美经验上的一个核心动作。因此,如果朱熹不再拘泥儒家伦理观,而能从儒家形上学的立场来思考,就可以融通邵雍的思想,扩大审美经验的范围与高度。[18]
(三)“悦乐”作为审美经验的最高境界
以儒家的观点人生乐处在于成德,或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朱子语类》提及“孔颜乐处”:
问:“濂溪教程子寻孔颜乐处,盖自有其乐,然求之亦甚难。”曰:“先贤到乐处,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学所能求。况今之师,非濂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着实用功处求之。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久久自当纯熟,充达向上去。”[19]颜回所乐之事不在于“箪瓢陋巷”本身,因为“箪瓢陋巷”其实对于颜回而言,是一种身心的考验,身处于一个物质条件简陋的环境,其简陋足以挠其心志,挫折其志向。而颜回仍然能不改其乐,在于他已经有了体道的经验,其快乐足以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种种不便。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美感经验的追求上,这种颜回之乐,也是符合美感经验的最高境界的。
或问:明道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则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横渠曰:“‘万物皆备于我’,言万事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诚’,谓行无不慊于心,则‘乐莫大焉’。”如明道之说,则物只是物,更不须做事,且于下文‘求仁’之说意思贯串。横渠解‘反身而诚’为行无不慊之义,又似来不得。不唯以物为事,如下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贯得为一意?”曰:“横渠之说亦好。‘反身而诚’,实也。谓实有此理,更无不慊处,则仰不愧,俯不怍,‘乐莫大焉’。‘强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诚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则近于仁矣。如明道这般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20]
对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表示我已无所需求,自身达至完满阶段。而且也不自欺,对自己诚实以对。这是最大可乐之事。综合所述,孔颜之乐在于“忘我”“忘忧”;“万物皆备于我”在于“完满”“充实”;“反身而诚”在于“行无不慊于心”,带来心境上的“心安”。这些源自进德修业的功夫,仍然适用于审美经验,因为美、善境界相合,可以达成“尽善尽美”。
在伦理行为上的“完满”,在于行为本身符合正道,符合人性之自然。在迈向行为的完善历程上,行为者必须借着感性的觉察与理性的判断来修正或验证行为的正当性。当一切符合伦理价值时,行为者感受到行为的完满而享受着实践伦理价值所带来的精神悦乐。而作为一位审美鉴赏者,则是从鉴赏主体默观被鉴赏对象的形象,直观到此形象与大道或“理型”的符合而得到心灵的悦乐。此行为上所践履的“大道”与心灵直观所见到的“大道”是同一的。儒家思想虽没有充分讨论审美的境界,但是由审美鉴赏与伦理实践的共同趋向,可以贯通伦理的悦乐与审美的悦乐,认为两者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我们便可以透过伦理上的悦乐来理解审美上的悦乐所带来的精神境界。[21]
四、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朱熹虽然没有明确地以审美为主题的论述,但是从他对感官经验的描述,可以运用于建立以朱熹思想为依据的审美观。在朱熹的大多数著述中,中心价值在于穷究天理与人性,与师友的讨论也多论及如何行善避恶,或如何读书的方法。整体来看是一种以伦理学为主轴的思想体系,并以天道观作为伦理思想的形上学依据。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也多是如此。但是,如何于人情、人欲上合理安排,仍是实践上必要的课题。经由感性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对美感经验的态度。基于美善同源的理由,我们可以尝试整理出一种儒家式的审美观,以对比于其他思想理论的审美观。
性是理抑或理气合
——朱子、阳明对孟子言“性”的不同理解
蔡家和
一、前言
宋明理学之兴起,其中朱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此因后续者,无论是宗朱或反朱,都多少与朱学相关;朱子继承程子之学而集大成,其编定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学者的必读之书[1],影响所及遍布东亚,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四书”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而朱子结合此四本书,并视此四者为道统的传承: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之后,汉儒无承继,此道统传跳而至程子,而朱子又是此道统的承继者,世称程朱理学。
朱子视自己是正统孟子的承继者,其《四书章句集注》对于孟子全文逐字逐句地一一注释。在朱子的年代,同时有象山兴起[2,象山属心学,而朱子属理学,双方批对方是禅学;朱子批象山教人不读书,沦为禅,而象山则批朱子求理于外,属义外,是告子之学,在“无极太极”之论辩时亦批朱子杂禅。二人所争辩的,则是谁人能够作为先秦儒学的继承者,真能承继孟子之学?
到了明代,阳明学兴起,亦是反对朱子的义外之说,视朱子格物穷理于外,非孟子的义内之学。阳明学的兴起,则是从其本身体证而来,原本视朱子为圣学的阳明,依于朱子之教而格竹子不得,最终于龙场体悟,发现格物致知原来不离于吾心,于是而有心学的倡议。阳明亦视己才是孟学继承人。此心学与理学的对抗,在《明儒学案》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两派都自认堪为孟学的正统。
本文主要比较朱子与阳明学的不同,并聚焦于二人于孟子性善论之诠解。朱子与阳明对孟子言“性”的见解不同,朱子继于程子,视性为“天理”,而认定孟子之论性而于气有所不备,“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3]。因为性只是理,于气上便有所不足,如朱子言:
《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4]朱子的性即理之说,认为人性与物性于天理处相同,都是仁义礼智,但于气禀的分受不同,人能全其理,而物只能表现其部分。人性、物性皆善,因为都是理,只因气禀的不同而于气质之性上有少异,于是认定在这之中便要加入形气之说始足,而孟子本人则少了此气的转语。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5],一者为天地之性,此性即理,另一性乃此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人性与物性在天理处相同,但在气质之性上始有不同。
以上看出朱子有二性之说,并以性即理为提纲,视孟子的性善是即于天理的性,此性为仁义礼智之性;至于阳明的学说乃针对朱子学而起,朱子学的二元架构,阳明缝补之。朱子将工夫析分为二:先知后行,此知与行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朱子主张体用二元、形上形下二元,以及分判已发、未发为二,凡此,阳明皆一以贯之。[6]
至于“性”的议题,朱子视“性即理”,心可以具理,然心不是理;阳明却视心即性即理。阳明虽也有心即理之说,然而此心即理,是否绝于气呢?阳明视心即理即气,此心并不绝于气,同样地,阳明言性,亦是性即理即气。阳明的原文出处,后文详之。
于此可见,朱子有二性之说,此一性为天地之性,此中只有理而无气,至于气质之性,为理落于气中所表现出的性,如月印万川,万川所倒映出的月亮,不如本来月亮之光明,此即理一分殊,天理落于形气中而为气质之性。至于阳明的性义,则是把朱子的二元论性义合而为一,以理与气之相合以言性。朱子视性即理,而阳明视性是理、气合,孰是孰非?在此将以孟子的原意来评论。[7]
二、朱子论性
朱子的二性之说始于程子,而朱子集大成而发扬理学,认定孟子于“气”有所不备,此指孟子于气讲得不足而需增补,于是朱子补了形下之气,此为气质、气禀,然此气与理不离不杂,性理与气的相加而为气质之性,乃天理落于气质之中者。朱子于《论语》注“性相近,习相远”处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
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
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8]朱子认为,孔子所言“性相近”之性,乃气质之性,而非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有美恶之分,岂能言“相近”?美、恶之相反犹若冰与炭,但溯于其初,还是可谓相近。朱子的意思是,其初不甚相远;美恶者,于其初时并未相反若此。气质之性之所以相差甚多,乃后天之习染所造成,故朱子所言的气质之性,一方面指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之中;另一方面,此气质之性与习相关。然依朱子后的学者,认为气质之性与习应该要做区分,而朱子未有区分,因为性是生而有之,习是后天习染,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两者是该区分。黄宗羲认为:
此章(富岁章)是“性相近习相远”注疏,孙淇澳先生曰:“今若说富岁凶岁,子弟降才有殊,说肥硗雨露人事不齐,而谓麰麦性不同,人谁肯信?至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就形生后说。若禀气于天,成形于地,受变于俗,正肥硗雨露人事类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谓习耳。今不知为习,而强系之性,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9]
黄宗羲注《孟子富岁子弟》章,引孙淇澳的见解,黄与孙两人认为性与习该做区分,性者生而有之,习者,后天也。而朱子把气质之性与习两者混在一起了。然而朱子论性,为何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从程子而来,程子的理由是“性即理”,性是仁义礼智,性之为体,体中也只有仁义礼智,此是性,也是天理,此天理在人,人人相同,不该言相近。而孔子何以言“性相近”?乃因为此处是就气质之性而言,非就本然之性言。故在程朱而言,天地之性,人人相同,都是天理;气质之性,则有美恶之不同,但在其初处,还是相近的。
于此看出朱子对于性的二层区分,有相同之性,此天地之性,性之本也,另一是气质之性,此性与气相混而成。朱子的二层区分,在注释《孟子》的《生之谓性》章处亦表现无遗: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10]
朱子认为,孟子言性是天理,此为形上,此性只有理而无形下之气。至于告子所言“生之谓性”,乃是天之气,而不是理,此为形下。而人物之生,亦有其形上之理,也有形下之气,因为理气不离不杂。此所谓的形上之理,人物皆有之,而人物之不同,在于气禀的差异,人能得其全,物得其偏,此偏、全者,就其能否实践道德之偏全而言,人能道义全具而能实践,动物道义亦全具,然气禀不佳而不能全之,只能表现其偏。
就其气言,人与物都有其知觉运动;就其理言,人物亦都有仁义礼智,但人能全之,物则不能。而人性之所以为无不善,为万物之灵者,乃在于人道义全具,故能付之实践以表现之,动物则只能表现其一部分,不及于人。而告子的差错在于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当之。可见朱子所认定的性可以有两层,上一层为天地之性,此性只有理,而无气,另一层是所谓气性,此气性,如告子所言,以气当之,所谓的生之谓性、食色之性,此所谓的中性材质义之性,而非无不善的本然之性。[11]
在朱子而言,《告子上》的前四章,告子所言之性皆只是形下的气性,未及于形上的必善之性;而于朱子所注的《告子上》前四章,并论及荀子、扬雄、佛氏、告子等人皆如此,所言之性皆是气性,而只有孟子论性是正确的,其视性善之性是形上之性,是天理,而其他人则皆误认气为性,只知饮食男女,而不及于道德。亦是说,荀子、告子等人只知于知觉运动的动物性,此动物性中不具道德性,唯有孟子能够指出道德性。虽人亦有动物性,然孟子不以动物性为性,虽不完全反对动物性,不反对好色、好货之心,然孟子心目中的性乃是以形上之理、道德性为主。
如果再看朱子于《性无善无不善》章所举者更为清楚。朱子举前人之言来做说明,其言: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
这里举了两段程子的话、一段张子的话,都认定性有二,一为天地之性,一为气质之性,而君子以天地之性为第一性,此乃性善之本。又程子之言表示,性与气二者要兼备始可。
然而,这是孟子的本意吗?孟子所言性若早已有气质于其中,则不消如程子一般,言性善若不补个气则为不备(程子先于性中脱落了气质,于是说孟子不备,又自行补上)。孟子的性善若早有气于其中,则不用如程子先把性中的气划分掉,然后说天地之性只有理而无气,因此有所不备,需要再补个气。若是阳明则于性中不脱落气,下文详之。
程子将性与气划分为二,论性,则只是理,而有不足,故要加气以补不足。至于第二段程子的说法,以性与才相比,此性即理,系出于天,而才禀于气,故其定义之才与孟子的才义不同。[13]程子的才是所谓的气禀、气质之性,故程子以性与才作为一相对待概念,其实也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区分。
从以上引文皆可看出,朱子论孟子性善区分了二性,亦可视为程朱理气论的变形,天地之性为理,而气质之性是理带有气。所谓天地之性之为理,亦可言之为理性,或是道德性,至于气质之性则指食色之性、生之谓性等。而朱子以二元区分来看待孟子之性论,阳明并不同意,下文明之。
三、阳明论性
若总结阳明之论孟子性善义,可谓性是理气合,一方面,阳明认为心即性即理,故“性即理”亦可接受,而另一方面,阳明言性又不只是理,尚且是气,故性为理气合。在《传习录·中卷》《答周道通书》有如下对话: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
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
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14]
周道通的疑惑是,程子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不知所指者何?其实,“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有人视为受有禅学“本来面目”影响,如黄宗羲即是如此;“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者,乃指本然之性,此系言语道断,如道之不可道;若一旦可说,则不是本然之性了,而是本然之性落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故曰:“才说性已不是性。”一旦说性,则落为气质之性,而不是性之本然矣。而朱子认为,“不容说”者,指人尚未出生之际,尚未具体成为人的气质之性;而曰“不是性”者,乃因不是本然之性,而是本然之性杂于气质之中,而为气质之性。
上引文中,一方面是周道通的疑惑,一方面也是程朱的回答;于此见出,程朱都有两层性论的意思。至于阳明则不然,阳明面对朱子的二元区分,总是缝补之,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缝补;如朱子的工夫之诚明两进[15],阳明则以致良知之本体工夫一以贯之。如今朱子的二性之说,在阳明则以一性通贯之,主张心即性即理。
然而性之即于理,是否即于气?理者,可视为道德之谓;气者,可谓为食色之性等。阳明言生之谓性,生者就气言,所谓的生理欲望、饮食男女等,此语是告子所言,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又谓“食色性也”,而阳明认为此“生”字与气有关,故气即是性,性即是气。至于阳明之解程子“才说性已不是性”,是认为一旦说气即是性时,则仅谈到气性一边,而未有性理。亦是说,依于阳明之见,性即理即气,但若只强调气的一面,则偏于气,而不及理,故不是性之本源;但若只强调本源而不及气,亦不可。孟子之言性固然是从本源上说,乃视性即理,然性只有理而无及于气乎?人性中只有道德,而无形色饮食等乎?阳明也不认为如此,而是性即理即气,理为本,而气为辅,此才是性。
故阳明言性善须在气上始见得,离气也无所谓性。恻隐、羞恶等在阳明视之为气;在朱子也视之为气,是情。然朱子是理气二元,形上形下二元区分,而阳明是理气一滚,形上形下相连。既然阳明言性是理气一滚,又将如何解释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说?
其实这句话,是由朱子真正继承,而阳明也自许可以继承于北宋精神,故其认为有些人只认得性理的一边,而有些人只认得气性一边,这都有所不及。视性为理者,只见道德性,而排斥饮食男女、情感等;视性为气者,却不及于道德。所以最后阳明认为性即气,气即性,性中本有气,非如朱子的先以性即理而排斥了气,最后再补气质之性,把气加回来,而为气质之性。阳明之不同于朱子在于,阳明一开始便不把气排除在性之外,性中本有理、有气,理气相即而为性,性是理气合。于此可见阳明论性与朱子不同,朱子所谓的性善是只有理而无气,而阳明认定的性善是理气相合。
以上讨论了阳明与朱子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见解,以下以孟子原文为标准,视二人谁人得孟子之意。
四、孟子论性
以上二位大儒之相争,对于性的见解不同,然而谁人为正?其实二位儒者都是在诠释孟子的性善论,故以孟子为标准则可判定谁人合于孟子。若如此则必定要回到孟子原文中始可判别。至于一旦谈到孟子的原文时,不知觉地必涉及诠释,本文在此希望尽量少些个人之诠释,而让孟子原文、原意展现出来。接下来,可以先看孟子的《富岁》章: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孟子于此所言的性是什么?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也。”圣人有其人性,一般人也有人性,人与人之间未有不同,圣人能充尽之,一般人亦可充尽之,如同都是麦,若人事稼耕上,其土壤相同,培育时间上相同,则培养出来的结果便能相近。
孟子此章尚有两个重点,第一,孟子言“举相似”,虽孟子于此章亦言“相同”,如“同嗜焉”“同听焉”,但其所谓的相同,应该是相似的意思,如同孟子言“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足之相同,是指其相似,足的大小是相近的,而不会相同;同样的,人的口味亦是相近,而不是相同。
第二,孟子于此所言之性为何?孟子言:“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犬马其性所好的口味,与人性的口味亦不相同,因其不同类所造成,牛好细草,而人则嗜炙,从于易牙之味。故在孟子而言,所谓的人性虽以仁义内在为人性,但人性不止于此,人性如同人这一类的本性,其口之于味者亦是性,故人性中有道德、有食色,此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纵是动物性中,人与动物亦不全同,人好西施,而物不好西施。[16]于此可见,人性中不只有道德性,而是道德性与动物性同处于人性之中,故孟子言:“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是指口之于味也是人的本性,乃因着运命气数之不齐,而不能必得之,于是君子视此则可有可无,不要求于必得之。
于此而知,阳明与朱子论性,阳明以性是理气合,较符合孟子,而朱子以性即理的看法,与孟子相去较远。朱子补回一个气质之性,也许可弥补此差别,然于本源处,认定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更无食色之性,一分一合之间,已是多此一举。
再举《食色性也》章为例,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如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
告子谈“食色性也”,亦谈“仁内义外”,至于孟子的回辩则只强调义者不在外,而是义内。谓仁内者,孟子也同意,至于食色性也,孟子亦无辩,不只无辩,而且在文末更以饮食来驳告子,看出孟子并不反对食色之性。
整篇论旨,告子视义为外,而孟子视义为内。然而告子所言外者,以义者为外,指道德的当宜者在于外,所谓的“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指的是长者为外在,而不是我能决定的;而孟子认为长之者才是义,非以长者为义,故视为内。何者为内呢?内是指吾人所生而有之者,在于我身上。仁何以是内?乃因仁是爱人,爱人从爱亲开始,故秦人之弟不爱,而吾弟则爱,此亲情血缘之关系,而为内,故仁之为内,孟子、告子都能同意。
至于义者,孟子视之为内,而告子视之为外,因为孟子视长之者为义;而告子视长者为义,因“彼长而我长之”,故彼长者,非于我也,是外在的。而孟子视仁义礼智为内,为性,是生而有之,内在本有的。然孟子论性善为内,为固有、本有,并不只有仁义是本有,而且人性中除了仁义之性外,亦有食色之性,告子承认了食色之性,故孟子以饮食之嗜炙以喻之。[17]内者,本有也,亦是人性,人性中有仁义,亦有动物性的饮食与生理欲望,只是人的饮食与动物的饮食亦不甚相同。人所喜好的是易牙所煮之食,人喜好的是烧烤之炙。而告子于论辩中,以秦人之弟则不爱,以仁为内,而爱自己兄弟;而以长楚人之长,亦长吾家之长,以长为悦,此悦不在我,而在对象,与吾弟之爱为血缘者不同。血缘是内在者故为内,有血缘者则爱,无血缘者则不爱。至于义,则无关于血缘与否,则以外在的长或不长为标准,故告子视之为外。
孟子最后只好举出人性中的饮食亦为内,亦是人性的一环以回辩,无论嗜谁人所做之炙,都喜欢,且此之爱炙者不从外来,而且是生而有之,是人这一类特殊的饮食习惯。亦是说告子认义为外,而孟子以饮食为内以辩之,论辩义内或外者,为何与饮食有关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此“内”的意思就“性”而言,乃生而有之,人性生而有仁义,亦有特殊饮食性,故孟子以此折服了告子。这也说明,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食色,则性是理气混,而以阳明的意思近于孟子。若于人性中把道德性与饮食切割开来,则孟子此章变得不知所云,而之所以有意义,乃在于人性中,道德与饮食男女者皆于其中。
或可再参见《孟子·告子上》的另一章有着相同的义理,孟季子与公都子的对话代表着孟子与告子的对话,其曰: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此场景同于上一章孟子与告子的义内、义外之辩,而如今场景换为学生的论辩,背后所代表者,则是双方的师承即孟子与告子的见解。孟季子的意思,无论是敬弟、敬叔父,或是敬兄、敬乡人,都由外在位置决定,此为外而不为内,这与“彼长而我长之”的意思一样,乃是告子的义外之说,指的是道义的标准为外在所决定,非我内在之决定。外在决定者,之所以敬叔父者,因叔父年纪长,而敬叔父;敬弟者,乃因尸位之故,此皆为外在决定。但孟子的意思是,长之者才是义,而非长者为义,义是愿意恭敬之心,是在我而不在外。最后的论辩,因着公都子之说而折服了孟季子,此公都子亦是承于孟子的精神而来。
此章与上一章如出一辙,谈义内、义外的问题,最后都以饮食之内在而折服对方。表示人性中,仁义内在,此为人性,然人性之内在者,不只是仁义,饮食亦为内在。此饮食之为内在,为告子、孟季子所深知,故告子言:“食色性也。”而且最后孟子以饮食之内在,来证成了仁义亦内在,仁义与饮食,都是人性。如此才足以折服告子、孟季子。此都说明孟子论性中包括了道德与食色。
然孟子亦不反对食色之性,此为内在,何以孟子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章谈到: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孟子对于“生之谓性”的反对,乃因这是以“生”来定义“性”(“性”者,生也),然性是落实于类上的殊义,乃落于此类而为此类之本质,足以区别于他类者,而生则是存活、存在义,范畴较“性”义大得多,故两者不应做比配。白羽、白雪、白玉之白者,是共相;而犬性、牛性、人性,是殊相,三性都不同,不可以共相定义殊相。白羽、白雪、白玉者,如同所谓的“生”,是为共相范畴,都就其白色而提出共相;而生者,都就其存在而言其共相,万物皆生。至于性,则有其分殊性,故万物之性不同,不可浑沦无别于人性、牛性与犬性,人性与牛性不同,牛性、犬性亦不同,人能实践道德,人性善,动物则无,人的饮食之性与牛的饮食亦不同。此乃“生之谓性章”的义理。孟子并不是反对形下气质之性,而是认为“生”与“性”之间关系的不对等,不可混而同之,更不可以生定义性。
除此之外,孟子亦言“形色天性”[18],乃是指人性中道德是为人性,饮食亦是,人的形色亦与他类不同。故人性中有道德,亦有饮食之特殊性,有其身体与他类之不同。人的形色与动物的形色不同,此为天性所赋予。
然而,孟子既然以人性中的饮食为重要,为何又要批评饮食?亦视耳目为小体?孟子对饮食之人曾有批评,原文如下: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
饮食之人而为人所贱者,因其养小而害大,若饮食作为养小而培育大,则饮食也不当被轻贱。所谓大者,大体也,心官也;小者,小体也,耳目之官也。耳目之官不需被反对,耳目之官是在不思而蔽于物时才有恶。恶是习所造成(也是从于小体所造成,此从者,心官从之)[19],本该性善,形色天性皆为善,耳目之善乃能听从于大体而做善事,如今因蔽于物,为习所染,故有恶,而恶者非耳目之官所该负责,而是蔽于物所造成,是习染所带坏,即因此心官不思而接受恶的习染所致。所以孟子此段最后言:“饮食之人,无有失也。”若饮食之人无失,无以小害大,则饮食之滋养却是应当的。孟子亦饮食,唯其饮食不以小害大,大者,心官之思诚而有德,而饮食正好用以照顾身体,用以实践道德,不妨害大者。饮食、食色者,亦是人性的一环,不可偏废。
面对齐宣王所言“寡人好色、好货”等弊病,孟子的回答是:“于王何有?”其认为好色又何妨,有此则能有其同理心。人这一类的人性就有其人性上的生理需求,此生理需求亦不同于动物,人好西施,动物则不好。于此好色处指点其为人性,则百姓亦为人,亦有人性,则亦需要结婚,故孟子指点若能推己及人,以同理心体会民心,则能行王道,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由此人性而能推己及人,透过小体用以实践大体。
形色都是睟面盎背的表现,形色即于天性,天性中的道德因着食色而能养,而能表现,此即孟子性善论之正义。性者,身体与道德都结合于其中,理气合于其中。若如此诠释孟子的性论,则可知,朱子、阳明对于人性见解的比较,则阳明以性是为理气合的说法较合于孟子,至于朱子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掉,而说孟子不备于气,然后又帮孟子补一个气质之性,可谓多此一举,虽无大错,然一分一合之间,性义枯矣。
五、结语与反思
本文讨论孟子的性义,以及朱子与阳明二人相关诠释何者较合。朱子与阳明常都用自己的体系套于经典,迁就古人以合于自己,可谓“六经”皆我脚注!而本文在此只谈孟子的性义,其他省略。文中谈到,朱子视性即理,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无孝悌,更无食色之性,而阳明认为性是理与气的结合(船山也认为性是理气合)。此理者,道德性也,气者,形色也,食色也。而最后判之以孟子原文,以评二人谁能较得孟子原意。文中举了《孟子·告子上》诸章为论证。本文认为,孟子所言性不是只有道德性,也包括食色之性,也包括形色天性,这些都善,动物亦有形色,然不能助之以成就道德,故动物身体亦无所谓善,而人的形色可成就德性,亦为天性,亦为善。而朱子却视性即理,把气质部分去除,阳明则未去除,故阳明得之,朱子未得之。
本文认为,孟子论性之义,为阳明较能合之。朱子之所以认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此有其时代的需求,一方面,需面对当时时代的需要,如魏晋所发展的才性之学、佛学的无明习之说,另一方面,也结合了佛学的贬低食色的见解,然此应非孟子本意。再者,朱子的二性之说也不合于孟子,孟子未有二性之说。又朱子言性,视人性、物性皆可为善,这也是创造性的诠释,孟子的性善是指人性善,犬牛则无,犬牛虽无善,但犬性还是不同于牛性,非可把此二性泛同之。朱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与物的区别是成就道德的全与偏之区别,此亦朱子的创造性诠释。朱子对于习的说明太少,系以气质之性言之,无论先天、后天都以气质之性来定义,然性既是生而有之,则与习应有区别,此朱子浑沦之处。
然朱子亦非全错,只是他先把性中的气质部分去除,而后再补气质之性回去,此分合之际,实是多此一举,而性亦枯槁矣。依于原文,孟子其实并未太多反对饮食男女,而是反对不依大体的饮食男女、以小害大的饮食男女,若饮食得其正者,孟子亦正视之,口之于味亦是性,形色亦是天性,此儒家对于食色之看法,而与佛家有别,不用贬低饮食男女之事,只要得正则可。
附注
注释:
[1]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2]苏文曰:“近来出土有一篇刻于698年的唐代墓志铭里出现‘道统’两字,题为《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详见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84页。
[3]钱大昕:“道统二字始见于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其第一图曰《传道正统》,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书成于乾道壬辰,与朱文公同时。”见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陈荣捷:“朱子实为新儒学创用道统一词之第一人。”见陈荣捷,《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此外,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彦寿,《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页,均持此说。
[4]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5]苏费翔,《宋人道统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6]蔡涵墨,《历史的严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6页。
[7]同上注,第107页。
[8]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58页。
[9]同上注,第458~459页。
[10]同上注,第459页。
[11]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525页。
[12]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13]苏费翔,《宋人道统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4]同上。
[15]苏费翔,《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载于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16]李心传,《丛书集成初编》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页。
[17]蔡涵墨,《历史的严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5~106页。
[18]同上注,第107页。
[1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0页。
[2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页。
[21]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2]同上。[23]朱熹,《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4]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9页。
[25]朱熹,《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06页。
[26]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2页。
[27]朱熹,《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16~1018页。
[28]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4页。
[29]朱熹,《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13页。
[30]李心传,《丛书集成初编》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
[31]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40页。
[32]同上注,第638页。
[33]束景南,《朱子大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4页。
[34]朱熹,《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38页。
[35]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39页。
[36]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元晦》:“《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吕祖谦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0页。
[37]《伊洛渊源录》一书至朱子离世都没有正式刊行过,但坊间出现一些盗版。
[38]朱熹,《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247页。
[39]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14页。
[40]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41]苏费翔,《宋人道统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2]如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即认为:“道统论其实就是朱熹所描绘的思想史,其对先人地位的勘定,与其说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还不如说是从朱熹的视角出发加以润色的结果,其中呼之欲出的就是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张己说。”见〔日〕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5~466页。
[43]朱熹,《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427页。
[44]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40页。
[45]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46]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47]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13页。
[48]同上注,第3639页。
[49]同上注,第3640页。
[50]同上。
[51]同上注,第3803页。
[52]同上注,第4050~4051页。
[53]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66页。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AZD032)。
[1]《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06页。
[2]《读论语孟子法》,《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3]《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语孟集义序》,《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31页。
[4]《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5]同上注,第14页。
[6]同上注,第16页。
[7]同上注,第17页。
[8]《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9]同上注,第30页。
[10]同上注,第34页。
[11]同上注,第33页。
[12]同上注,第29页。
[13]《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14]同上注,第243页。
[15]《尽心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59页。
[16]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7]周炽成,《唐宋道统新探》,《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18]《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四,《居士集叙》,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16页。
[19]程颐,《明道先生墓表》,《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40页。
[20]《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1]《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2]《尧曰第二十》,《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十,《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23]《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4]《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25]《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6]《论孟集义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31页。
[27]《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
[28]《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9]《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30]《大学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5页。
[31]《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2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4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注释:
[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三卷第二部分以及结束语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篇第八章第一、二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3]李景林,《孔子“闻道”说新解》,《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
[4]《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二,《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8页。
[5]韩愈,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50页。
[8]张伯行,《续近思录》,收录在《近思录专辑》第5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1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黄百家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2页。
[11]《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12]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13]《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86~3587页。
[14]《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26~3627页。
[15]《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5页。
参考文献:
〔1〕李景林,《孔子“闻道”说新解》,《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
〔2〕韩愈,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
注释:
[1]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7页。
[2]孔颖达,《文言传·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
[3]同上。
[4]同上。
[5]程颐,《遗书》卷十五,《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8页。这里对文中“信”的解释,均参照括号内(原文为小号字)文字。
[6]程颐,《遗书》卷九,《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5页。[7]程颐,《遗书》卷十五,《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4页。
[8]程颐,《周易程氏传·文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9页。
[9]程颐,《周易程氏传·乾》,《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
[10]程颐,《遗书》卷十九,《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
[11]程颐,《周易程氏传·乾》,《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
[12]程颐,《周易程氏传·文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7页。
[13]韩愈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见《原道》,《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72页。韩愈这里既是对儒家“道德”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老子》失道德而后有仁义的去仁义的“道德”观。
[14]程颐,《遗书》卷十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15]程颐,《遗书》卷二十一下,《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4页。
[16]程颐,《遗书》卷十八,《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4页。
[1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06页。
[1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3页。
[19]程颐,《周易程氏传·文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9页。
[2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76页。
[21]朱熹云:“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见《论语集注·学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22]朱熹,《论语集注·学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23]同上注,第466页。
[24]同上注,第468页。
[25]同上注,第466页。
[2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112页。
[2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3页。
[28]同上注,第463页。
[29]同上注,第467页。
[30]同上。
[31]朱熹,《仁说》,《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册,第3280页。
[32]同上注,第3279页。
[33]同上注,第3279~3280页。
[34]朱熹,《文言传》疏,《周易本义》,苏勇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71页。
[3]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9页。
[4]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页。
[5]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6页。
[6]何亦凡,《敦煌吐鲁番出土<郑玄论语注>“束修”条缀补复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9页。
[7]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1页。
[8]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页。
[9]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6页。
[10]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六,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97页。
[11]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07页。
[12]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9页。
[13]毛奇龄,《四书剩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1~222页。
[14]方观旭,《论语偶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15]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8页。
[16]同上。
[17]黄式三,《论语后案》,《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83~484页。
[18]何晏、邢呙,《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2页。
[19]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1页。
[2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5页。
[2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四,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1页。
[22]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43页。
[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2页。
[24]同上。
[25]同上注,第72页。
[26]同上注,第78~79页。
[27]同上注,第92页。
[28]同上注,第167页。
[2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四,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1页。
[30]朱熹,《论孟精义》,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31]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43页。
[3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5页。
[3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四,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1页。
[34]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十一,《船山全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485页。
[35]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5页。
[36]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注释:
[1]也有一些学者对这套话语体系进行了审视与反思,见〔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
[2]真德秀,《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3]朱熹,《答罗参议》,《朱文公续集》卷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
[4]同上注,第4747页。
[5]张栻,《答朱元晦秘书》,《南轩集》卷二十三,杨世文、杨蓉贵点校,《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875页。
[6]张栻,《答陆子寿》,《南轩集》卷二十六,杨世文、杨蓉贵点校,《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920页。
[7]朱熹,《中和旧说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34页。
[8]朱熹,《答许顺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45页。
[9]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子年谱》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页。
[10]朱张关于太极的讨论依旧与中和已发未发密切相关,参见王懋竑,《年谱考异》卷一,何忠礼点校,《朱子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6~307页。
[11]张栻,《诗送元晦尊兄》,《南轩集》卷一,杨世文、杨蓉贵点校,《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533页。
[12]朱熹,《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朱文公文集》卷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
[13]朱熹,《自论为学工夫》,《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35页。
[14]朱熹,《与曹晋叔书》,《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9页。
[15]朱熹,《答程允夫》,《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1页。
[16]朱熹,《答石子重》,《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2页。
[17]朱熹,《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朱文公文集》卷五,《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页。
[18]朱熹,《祭张敬夫殿撰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74页。
[19]朱熹,《又祭张敬夫殿撰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75~4076页。
[20]张拭,《答陆子寿》,《南轩集》卷二十七,杨世文、杨蓉贵点校,《张拭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920页。
[21]张栻《寄吕伯恭》,《南轩集》卷二十五,杨世文、杨蓉贵点校,《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892页。
[22]张栻,《上封有怀元晦》,《南轩集》卷四,杨世文、杨蓉贵点校,《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23]陈亮,《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页。
[24]辛弃疾,《东莱先生祭文》,《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卷二,《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3页。
[25]叶适,《皇朝文鉴》,《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95页。
[26]叶适曾就他所认可的儒者群体说:“每念绍兴末,陆九渊、陈傅良、陈亮,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六,《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6页。
[27]周必大,《吕伯恭》,《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28]陈亮,《钱叔因墓志铭》,《陈亮集》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0页。
[29]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3页。
[30]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楼钥集》卷五十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70页。
[31]赵善下,《祠堂奉安州郡祭文》,《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拾遗,《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23页。
[32]周密,《道学》,《齐东野语》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
[33]韩淲,《涧泉日记》卷中,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34]李心传,《道学兴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8页。
[35]丁端祖,《东莱先生吕成公覆谥议》,李心传,《道命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36]丁端祖,《陆象山先生覆谥》,《陆九渊集》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7页。
[37]方大琮,《与周连教梅叟》,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三八五,第32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
[38]家铉翁,《敬室记》,《则堂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1页。
[39]刘宰,《通鹤山魏侍郎了翁》,《漫塘文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9页。
[40]吕中,《仁宗皇帝》,《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十,《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41]魏了翁,《答刘司令宰》,《鹤山文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2页。
[42]魏了翁,《孙氏拙斋论孟序》,《鹤山集》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0页。。
[43]真德秀,《先贤祠》,《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09页。
[44]黄榦,《复林自知》,《勉斋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45]黄榦:《朱先生行状》,《勉斋集》卷三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
[46]陈埴,《近思杂问附》,《木钟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03页。
[47]熊禾,《三山郡泮五贤祠志》,《勿轩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1页。
[48]程端蒙、程若庸,《治道第六》,《性理字训》,徐梓、王雪梅编,《蒙学辑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49]陈淳,《严陵学徙张吕合五贤祠说》,《北溪大全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5页。
[50]陈淳,《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2页。
[51]真德秀,《先贤祠》,《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09页。
[52]陈淳,《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2页。
[53]陈淳,《与姚安道》,《北溪大全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43页。
[54]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北溪大全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5页。
[55]程端礼,《送刘宗道归夷门序》,《畏斋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9页。
[56]胡助,《纯白先生自传》,《纯白斋类稿》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4页。
[57]陈栎,《答问》,《定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0页。
[58]梁寅,《道学》,《策要》卷六,嘉庆宛委别藏本。
[59]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吴文正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
[60]吴澄,《答田副使第三书》,《吴文正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54页。
[61]杨廉,《白鹿洞宗儒祠记》,《杨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九,《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62]章懋,《复贺黄门克恭钦》,《枫山集》(外四种)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页。
[63]李东阳,《重建岳麓书院记》,《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八,吴道行、赵宁修纂,《岳麓书院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02页。
[64]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八,吴道行、赵宁修纂,《岳麓书院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03页。
[65]黄宗羲,《南轩学案》,《宋元学案》,《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53页。
[66]杭世骏,《礼部尚书张公伯行传》,《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二,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2页。
[67]彭时,《大学士彭时修学记》,杨林,《长沙府志》卷四,明嘉靖刻本。
[68]戴铣,《朱子实纪年谱》卷一,《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注释:
[1]吴展良,《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438~441页。
[2]朱熹,《四书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第9页。
[3]黎敬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75页。
[4]同上注,第9页。
[5]同上注,第1026页。
[6]朱熹,《四书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第44页。
[7]黎敬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79页。
[8]同上注,第879~880页。
[9]朱熹,《四书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第59页。
[10]黎敬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22页。
[11]朱熹,《四书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第19页。
[12]黎敬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5~636页。
[13]同上注,第431页。
[14]同上注,第498页。
[15]同上注,第2544~2545页。
[16]同上注,第317页。
[17]同上注,第700页。
[18]黄俊杰、林维杰,《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第6~8页,第12~14页;蔡振丰,《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83、92页。
[19]黎敬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99页。
[20]同上注,第1437页。
[2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201页。
参考文献:
〔1〕吴展良,《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2〕朱熹,《四书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
〔3〕黎敬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黄俊杰、林维杰,《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
〔5〕蔡振丰,《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
〔6〕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作者单位: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
注释:
[1]从元代起,科举考试以朱子的诠释为定本。
[2]象山自言,其心学的兴起为读《孟子》而自得之。
[3]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1388页。又“论性不论气”之原文出自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第1册,第81页。
[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5]虽然说朱子论性亦可以只是一性,如言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落在气中,然而朱子的性即理之说,与孟子的见解还是不同。
[6]如阳明谈已扣之钟是寂天寞地,而未扣时是惊天动地,则是把已发与未发合而为一。
[7]孟子本身其实亦无所谓的理气论,用理气论以评孟子,是以后人的观点回溯之。例如,孟子言理之处甚少,只有“始条理”“终条理”“理义之悦我心”几处。至于孟子言气,在《知言养气》章谈了一些“气”字,在《牛山之木》章谈“养夜气”“平旦之气”,在《孟子自范之齐》章言:“居移气,养移体”,大致只有三章。而本文用理气以形容孟子,是采用宋明理学的概念来形容之,并不算准确,因为不见得是孟子自己的术语;因此本文再做定义,所谓理者,性即理,指的是道德的仁义礼智,指人性中只有道德的成分;至于性即气者,乃所谓的耳目口鼻等、食色之性的意思。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175~176页。
[9]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年,第1册,第137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326页。
[11]牟宗三言:“如是,则孟子心目中的性必不是中性的材料义之性。……然则何种意义的性始可看成是中性的材料,又何种意义的性始能自发出仁义而可被说是定善,这不可不予以辨明。”牟宗三,《圆善论》,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2页。牟宗三为当代新儒学,承继于宋学,而不承汉学,以二层的性论来诠释孟子,近于朱子之说。一种是必善之性,另一种是材质生理之性。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329页。
[13]孟子言“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才殊尔”,此二“才”字指的都是“性”。
[14]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第150条。
[15]此为先知后行的工夫。
[16]船山认为,人性的食色,与动物亦不同:“王嫱、西施,鱼见之而深藏,鸟见之而高飞,如何陷溺鱼鸟不得?牛甘细草,豕嗜糟糠,细草、糟糠如何陷溺人不得?”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066页。[17]焦循曰:“告子既知甘食为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见焦循,《孟子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5页。
[18]船山曾对于形色又是天性又是小体做一解释:“孟子以耳目之官为小体,而又曰‘形色,天性也’,若不会通,则两语坐相乖戾。盖自其居静待用,不能为功罪者而言,则曰‘小体’;自其为二殊五实之撰,即道成器以待人之为功者而言,则竟谓之‘天性’。”小体乃相对于心官为大,而不能居功或居罪言,至于天性者,乃于器中言道,人能用此官能而成就大事者言之。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071页。
[19]孟子言心不是皆为正,如言:“大人格君心之非”,则君心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则人心不正;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此心亦不正。故陷溺人心,心为甚,而不是只有小体陷溺之。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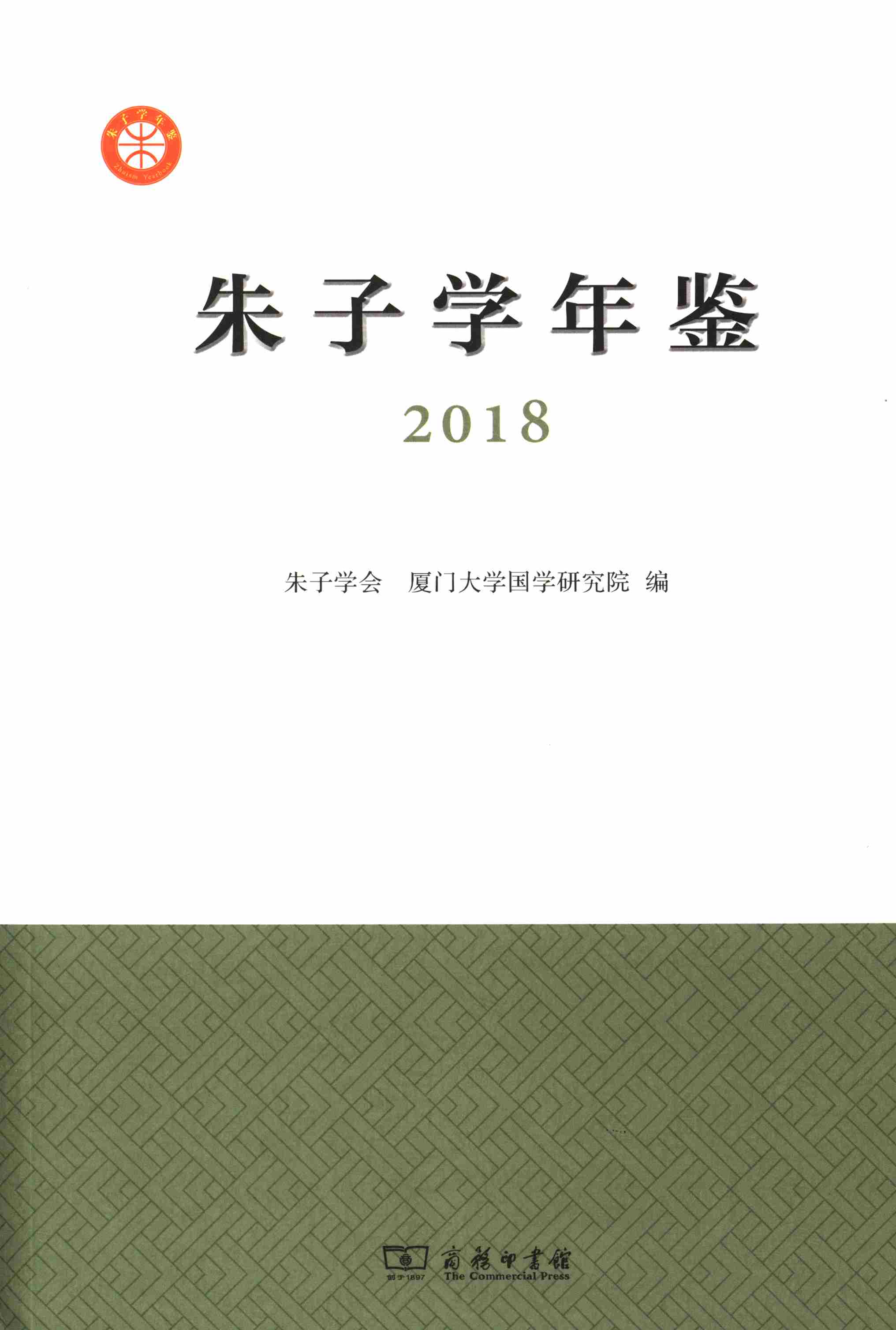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