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8)》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279 |
| 颗粒名称: | 特稿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6 |
| 页码: | 001-02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南平市的朱子学年鉴2018年的特稿,包括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的内容介绍。 |
| 关键词: | 南平市 特稿 朱子 |
内容
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
陈来
朱子于乾道己丑(1169)春中和之悟后,在将中和之悟报告张栻等湖南诸公的同时,即开始了他的哲学建构。当年六月他刊行了建安本《太极通书》,接着写作《太极图解》和《太极图说解》,二者合称《太极解义》。次年春,《太极解义》完成,他立即寄给当时在严州的张栻和吕祖谦,此后数年在与张、吕的讨论中不断修改,至乾道癸巳年(1173)定稿。
一、“太极”本体论
让我们先来看《太极图解》。由于图解的图形不易印刷,我们这里把代表太极、阴阳的图形直接转为概念,使文句明白通贯,便于讨论。
对于太极图最上面的第一圆圈,朱子注:
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1]
这是说第一圆圈就是指代《太极图说》的首句“无极而太极”,而落实在“太极”,因为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指“无形无象的太极”。朱子解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即把“本体”作为道学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这一“本体”概念在图解中反复出现,成为《太极图解》哲学建构的突出特点。这也是二程以来道学所不曾有过的。照朱子的解释,太极是动静阴阳的本体,此一本体乃是动静阴阳之所以然的根据和动力因。而这一作为本体的太极并不是离开阴阳的独立存在者,它即阴阳而不杂乎阴阳。“即阴阳”就是不离乎阴阳,“不杂乎阴阳”说明太极并不是阴阳,也不是与阴阳混合不分。这一“不离不杂”的说法开启了朱子学理解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存在关系模式。
对于太极图的第二圆圈,就是所谓坎离相抱图,他认为左半边是阳之动,右半边代表阴之静,而包围在中间的小圆圈则是太极。他指出,太极“其本体也”,意味太极是阳动阴静的本体;又说,阳之动,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阴之静,是“太极之体所以立也”。这就区分了太极的体和用,认为阳动是太极之用流行的表现,阴静则是太极之体得以定立的状态。按这里所说,不能说太极是体,阴阳是用,或太极是体,动静是用,也不能说阳动是太极之体,阴静是太极之用。因为,阴和阳同是现象层次,太极是本体层次,故不能说阳动是现象层次的用,阴静就是本体层次的体;只是说,阳动可以见太极之用的流行,阴静可以显示太极之体的定立。朱子《答杨子直书》说,他一开始曾经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后来不再用体用的关系去界定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出,在《太极解义》初稿写成的时期,朱子从《太极图说》文本出发,更为关注的是太极动静的问题,而不是太极阴阳的问题。阴阳是存在的问题,动静是运动的问题,本体与此二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朱子总论自上至下的前三图说:
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余欠也。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太极),无假借也。[2]这显然是依据《太极图说》的文字来加以解释,《太极图说》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3]《太极图说》本来就是阐发太极图的文字,朱子要为太极图作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太极图说》本身并加以解释,于是就难免和他的《太极图说解》有所重复。这里“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指明了“无极”的意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这比《太极图说》第一句的解释之所指,更为清楚。
图解接着说“乾男、坤女,以气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又说“万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4]。这和《太极图说》解也类似:“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5]不同的是,在图解这里的重点是区分“气化”和“形化”。
以下谈到圣人与主静:
惟圣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极)之体用也。是以一动一静,各臻其极,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动之中。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太极)于是乎立。[6]这里对圣人提出了新的理解,不是按照《太极图说》本文那样,只从“得其秀而最灵”的生理基础去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是从“全乎太极之体用”的德行来理解圣人的境界。即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够完全实现太极之用,完全定立太极之体。具体来说,是以中正仁义贯穿动静,而以静为主,于是“人极”便得以确立起来了。人极就是人道的根本标准,人极与太极是贯通的,人能全乎太极便是人极之立。
二、“太极”“动静”阴阳论
现在我们来看《太极图说》解。
周敦颐《太极图说》本身,最重要的是七段话,朱子的解义也主要是围绕这七段话来诠释的。
第一段,无极而太极。
朱子注: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7]这是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解释无极,用“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解释太极,并且强调,无极只是太极无声无臭的特性,并不是太极之外的独立实体。这就从根本上截断了把《太极图说》的思想理解为道家的无能生有的思想的可能性。这也就点出,《太极图说》在根本上是一太极本体论体系,或太极根源论的体系。“枢纽”同中枢,“造化之枢纽”指世界变化运动系统中其主导作用的关键。“根柢”即根源,“品汇之根柢”指万物的根源。枢纽的提法表示,太极的提出及其意义,不仅是面对世界的存在,更是面对世界的运动,这也是《太极图说》本文所引导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太极图解》第一段对太极所做的“本体”解释相比,《太极图说解》的第一段解释中却没有提及本体这一概念,也许可以说,在《太极图说解》中,“本体”已化为“枢纽”和“根柢”。前者针对动静而言,后者针对阴阳而言。
第二段,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注: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8]朱子《太极解义》的主导思想体现在这一段的解释。他首先用《通书》的思想来解说太极的动静,把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解为“天命流行”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一阴一阳往来变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也就是《通书》所说的诚之通和诚之复交替流行不已的过程,动是诚之通,静是诚之复,二者互为其根。
因此,《太极图说》的根本哲学问题,在朱子《太极解义》看来,就是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而不是像他晚年和陆九渊辩论时主张的,只把太极和阴阳的关系问题看作首要的问题。这是符合《太极图说》本文脉络的。在这个前提下,太极和阴阳的问题也被重视。因此,《太极解义》中最重要的论述是“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这两句话,先讲了太极和动静的分别及关系,又讲了太极和阴阳的分别及关系。就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言,《太极解义》的体系可称为太极本体论;就太极与阴阳的关系而言,此一体系可称为太极本源论。据朱子在写作讨论《太极解义》过程中与杨子直书,他最初是用太极为体、动静为用来理解太极与动静的关系,但后来放弃了,改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的关系。那就是说,他以前认为,太极是体,动静是太极所发的用,二者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这显然不适合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是本体和载体的关系,把动静作为载体,这就比较适合太极和动静的关系了。本然之妙表示太极既是本体,又是动静的内在原因(动力因),“妙”字就是特别用来处理与动静关系的、用来说明运动根源的,这也是中国哲学长久以来的特点。与《周易》传统以“神”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不同,朱子以“道”即太极作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
“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则明确用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区别太极与阴阳,即太极是形而上的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二者有清楚的分别。把太极明确界定为道,这样就与把太极解释为理,更为接近了。
“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著是显著的用,微是内在深微的体。从微的角度看,太极就是动静阴阳之理,在内在的体;从著的角度看,动静阴阳运行变化不同,是表现著的用。所以,朱子认为太极和动静阴阳还是存在着体用的分别。特别是,这里直接以太极为理,为动静阴阳之理,提出理和动静阴阳始终是结合一起的,强化了理的意义。朱子认为,既不能说从某一个时期开始理和动静阴阳二者才相结合,也不能说将在某一个时期二者将会分离。太极始终是内在于动静和阴阳的。本来,在宇宙论上,动静就是阴阳的动静,但由于《太极图说》讲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地说,动静就成为先在于阴阳、独立于阴阳的了。
第三段,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朱子注: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9]
如果说第二段的解释关注在动静,这一段的解释关注的中心则在阴阳。从太极的动静,导致阴阳的分化与变合;有阴阳的一变一合,则产生了五行的分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这是一套由阴阳五行展开的宇宙生化论。与前面第二段不同,这里对太极的定义不是从动静的枢纽来认识太极,而是从阴阳的所以然根据来认识太极。或者说,前面是从“所以动静者”来认识太极,这里是从“所以阴阳者”界定太极。“所以为阴阳者”的视角就是存在的视角,而不是运动的视角了。至于“太极之本然”,即是《太极图解》的“本体”,“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所以阴阳者”的观念本来自二程,区分“阴阳”和“所以阴阳”,认为前者是形而下者,后者是形而上者,这种思维是朱子从程颐吸取的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对照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和吕祖谦的《太极图义质疑》,可以明显看出朱子此时的哲学思维的优势,这也是何以张、吕对朱子解义的意见只集中在“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一句,而对其太极本体论、太极根源论、太极生化论并未提出意见的原因。
三、“太极”本性论
从第四段开始,由太极动静阴阳论转到太极本性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注:
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10]前面已经说过,宇宙中处处是阴阳,而凡有阴阳处必有所以为阴阳者,这就是“无适而非阴阳”“无适而非太极”。阴阳分化为五行,五行发育为万物,万物中也皆有太极,故说“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各具于事物之中的太极即是事物之性,太极就是“性之本体”,这就转到了万物的本性论。万物因气禀不同而造成“各一其性”,即各异其性、各有各的性,互不相同。“各一其性”是说明万物由气禀不同带来的性的差异性。但朱子同时强调,太极无不具于每一物之中,这才真正体现出“性无所不在”的原理。这样朱子的解释就有两个“性”的概念,一个是“各一其性”的性,一个是“太极之全体”的性,前者是受气禀影响的、现实的、差别的性,后者是不受气禀影响的本然的、本体的、同一的性。故每一个人或物都具备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但这种具备不是部分地具有,而是全体地具有。每一个人或物都具有一太极之全体作为自己的本性。这是朱子对《太极图说》自身思想的一种根本性的发展,即从各一其性说发展为各具太极说。
第五段,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朱子注:
夫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无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所谓“妙合”者也。“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矣。[11]
上段最后讲性无不在,这里接着把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也作为性无不在的证明。这就是说,气质所禀与二五之精相联系,太极本体与无极之真相对应,各一其性与各具太极混融无间,此即性无不在的体现。重要的是,此段明确声明:“‘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这就把无极之真,同时也把太极解释为“理”了,把太极和理贯通,由此打开了南宋理气论哲学的通途。当然,太极也仍被确定为“性”,“性为之主”本是胡宏的思想,这里显示出湖湘学派把太极理解为性对朱子仍有影响。这里的性为之主,也从特定方向呼应了太极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的意义。“以理言”和“以气言”的分析使得理气论正式登上道学思想的舞台。没有《太极解义》,朱子学的理气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哲学论述。
对照《太极图解》可知,太极本性论是朱子《太极解义》的重要思想。朱子强调,男与女虽然各有其性,互不相同,但男与女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男女一太极也”。万物各异其性,而万物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万物一太极也”。尤其是,这里提出了万物各具的太极与宇宙本体的太极的关系,朱子认为,“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是万物的存在总体,其存在的根据是太极,而每一个人或物,也具有此一太极为其本性。每个人或物对宇宙总体而言是分,但每个人或物具有的太极并不是分有了太极的部分,而是全体,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后来朱子在《语类》中反复申明了这个道理。如朱子与张栻书所讨论的,朱子认为“各具一太极”的说法意在强调“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用太极的概念来表达性理学的主张。
四、“全体太极”之道
以下开始转到人生论。
第六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朱子注:
此言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也。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然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而五性之殊,散为万事。盖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圣人全体太极有以定之,则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而违禽兽不远矣。[12]
“全”或“全体”是《太极解义》后半部的重要概念,是属于人生境界与功夫论的概念。朱子认为,人物之生,皆有太极之道,此太极之道即人与物生活、活动的总原则,也是人与物的太极之性的体现。物所禀的气浑浊不清,故不能有心,亦不可能实现太极之道。只有人独得气禀之秀,其心最灵,才有可能使人不失其太极本性,体现天地之心,确立人极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皆能如此,唯有圣人能“全体太极”,即完全体现太极,完全体现太极之道和太极之性,真正确立人极。这也就是下段所说的“定”和“立人极焉”。
第七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注: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而圣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若程子论乾坤动静,而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亦此意尔。[13]
《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开始,以人极为结束,而人极的内涵是中正仁义而主静,中正仁义是基本道德概念,主静是修养方法,以人极而兼有二者,这在儒学史上是少见的。但《荀子》中也谈到静的意义,《礼记》的《乐记》本来强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故“静”在儒学史上也曾受到注意,尤其是《乐记》的思想在宋代道学中很受重视,在这个意义上,主静的提出不能仅看作受到佛道修养的影响。但对朱子和南宋理学而言,必须对主静做出新的论证。
根据六、七两段的朱子注,他提出,众人虽然具动静之理,即具有太极,但常常失之于动,其表现是“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即欲望、情欲的妄动,对私利的追逐,必须以人极“定”之,“定”是对于“失之于动”的矫正,也是使人不至失之于动的根本方法。所以在朱子的解释中,静与定相通,一定要分别的话,可以说静是方法,定还是目的,这就是“于此乎定矣”。
在第六段朱子注强调“不失其性之全”“圣人全体太极”,在第七段,又提到“圣人全动静之德”“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全体”就是全幅体现,是一实践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全动静之德,是特就人对动静之理的体现而言,全动静之德的人,就不会失之于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行事中正仁义,因此全动静之德就是全太极之道,全体太极也就是全体太极之道,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在第七段之后,朱子还说:“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14]我们记得,在《太极图解》中也说过“全乎(太极)之体用也”,这些都是相同的意思。
当然,由于《太极图说》本文强调主静,故朱子也同意“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为什么要本于静、主于静?照朱子说,这是因为“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即是说,静是体,动是用,所以以主静为本。《太极图解》比《太极图说解》这里说得更具体:“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者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极)于是乎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朱子与张栻、吕祖谦做了反复的讨论。此外朱子也指出,主静所指的这种“静”不是专指行为的,而是指心的修养要达到“此心寂然无欲而静”。这当然是合乎周子本人主张的“无欲故静”的。
应当指出,朱子《太极解义》中在论及主静时没有提到程颐的主敬思想,只在一处提及“敬则欲寡而理明”,这对于在己丑之悟已经确认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宗旨的朱子,是一欠缺。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重视程门主敬之法,对朱子是一个重要补充。
五、《太极解义》引起的哲学论辩
朱子《太极解义》文后有《附辩》,其中提到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或谓)和三种次要的反对意见(有谓)。朱子简单叙述了这些意见: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15]
所谓“读者病其分裂已甚”,应是张栻的意见(张栻《寄吕伯恭》)。四个“或谓”中,第一个“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应是廖德明的意见(朱子《答廖子晦一》);第二个“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应是吕祖谦的意见(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第三个“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是吕祖谦的意见(张栻《答吴晦叔》),第四个“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应是张栻的意见(朱子《答张敬夫十三》)。至于“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应该都与张栻、吕祖谦的意见有关。
朱子在《附辩》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回应:
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陈来朱子于乾道己丑(1169)春中和之悟后,在将中和之悟报告张栻等湖南诸公的同时,即开始了他的哲学建构。当年六月他刊行了建安本《太极通书》,接着写作《太极图解》和《太极图说解》,二者合称《太极解义》。次年春,《太极解义》完成,他立即寄给当时在严州的张栻和吕祖谦,此后数年在与张、吕的讨论中不断修改,至乾道癸巳年(1173)定稿。
一、“太极”本体论
让我们先来看《太极图解》。由于图解的图形不易印刷,我们这里把代表太极、阴阳的图形直接转为概念,使文句明白通贯,便于讨论。
对于太极图最上面的第一圆圈,朱子注:
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1]这是说第一圆圈就是指代《太极图说》的首句“无极而太极”,而落实在“太极”,因为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指“无形无象的太极”。朱子解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即把“本体”作为道学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这一“本体”概念在图解中反复出现,成为《太极图解》哲学建构的突出特点。这也是二程以来道学所不曾有过的。照朱子的解释,太极是动静阴阳的本体,此一本体乃是动静阴阳之所以然的根据和动力因。而这一作为本体的太极并不是离开阴阳的独立存在者,它即阴阳而不杂乎阴阳。“即阴阳”就是不离乎阴阳,“不杂乎阴阳”说明太极并不是阴阳,也不是与阴阳混合不分。这一“不离不杂”的说法开启了朱子学理解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存在关系模式。
对于太极图的第二圆圈,就是所谓坎离相抱图,他认为左半边是阳之动,右半边代表阴之静,而包围在中间的小圆圈则是太极。他指出,太极“其本体也”,意味太极是阳动阴静的本体;又说,阳之动,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阴之静,是“太极之体所以立也”。这就区分了太极的体和用,认为阳动是太极之用流行的表现,阴静则是太极之体得以定立的状态。按这里所说,不能说太极是体,阴阳是用,或太极是体,动静是用,也不能说阳动是太极之体,阴静是太极之用。因为,阴和阳同是现象层次,太极是本体层次,故不能说阳动是现象层次的用,阴静就是本体层次的体;只是说,阳动可以见太极之用的流行,阴静可以显示太极之体的定立。朱子《答杨子直书》说,他一开始曾经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后来不再用体用的关系去界定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出,在《太极解义》初稿写成的时期,朱子从《太极图说》文本出发,更为关注的是太极动静的问题,而不是太极阴阳的问题。阴阳是存在的问题,动静是运动的问题,本体与此二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朱子总论自上至下的前三图说:
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余欠也。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太极),无假借也。[2]这显然是依据《太极图说》的文字来加以解释,《太极图说》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3]《太极图说》本来就是阐发太极图的文字,朱子要为太极图作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太极图说》本身并加以解释,于是就难免和他的《太极图说解》有所重复。这里“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指明了“无极”的意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这比《太极图说》第一句的解释之所指,更为清楚。
图解接着说“乾男、坤女,以气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又说“万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4]。这和《太极图说》解也类似:“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5]不同的是,在图解这里的重点是区分“气化”和“形化”。
以下谈到圣人与主静:
惟圣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极)之体用也。是以一动一静,各臻其极,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动之中。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太极)于是乎立。[6]这里对圣人提出了新的理解,不是按照《太极图说》本文那样,只从“得其秀而最灵”的生理基础去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是从“全乎太极之体用”的德行来理解圣人的境界。即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够完全实现太极之用,完全定立太极之体。具体来说,是以中正仁义贯穿动静,而以静为主,于是“人极”便得以确立起来了。人极就是人道的根本标准,人极与太极是贯通的,人能全乎太极便是人极之立。
二、“太极”“动静”阴阳论
现在我们来看《太极图说》解。
周敦颐《太极图说》本身,最重要的是七段话,朱子的解义也主要是围绕这七段话来诠释的。
第一段,无极而太极。
朱子注: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
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7]这是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解释无极,用“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解释太极,并且强调,无极只是太极无声无臭的特性,并不是太极之外的独立实体。这就从根本上截断了把《太极图说》的思想理解为道家的无能生有的思想的可能性。这也就点出,《太极图说》在根本上是一太极本体论体系,或太极根源论的体系。“枢纽”同中枢,“造化之枢纽”指世界变化运动系统中其主导作用的关键。“根柢”即根源,“品汇之根柢”指万物的根源。枢纽的提法表示,太极的提出及其意义,不仅是面对世界的存在,更是面对世界的运动,这也是《太极图说》本文所引导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太极图解》第一段对太极所做的“本体”解释相比,《太极图说解》的第一段解释中却没有提及本体这一概念,也许可以说,在《太极图说解》中,“本体”已化为“枢纽”和“根柢”。前者针对动静而言,后者针对阴阳而言。
第二段,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注: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8]朱子《太极解义》的主导思想体现在这一段的解释。他首先用《通书》的思想来解说太极的动静,把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解为“天命流行”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一阴一阳往来变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也就是《通书》所说的诚之通和诚之复交替流行不已的过程,动是诚之通,静是诚之复,二者互为其根。
因此,《太极图说》的根本哲学问题,在朱子《太极解义》看来,就是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而不是像他晚年和陆九渊辩论时主张的,只把太极和阴阳的关系问题看作首要的问题。这是符合《太极图说》本文脉络的。在这个前提下,太极和阴阳的问题也被重视。因此,《太极解义》中最重要的论述是“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这两句话,先讲了太极和动静的分别及关系,又讲了太极和阴阳的分别及关系。就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言,《太极解义》的体系可称为太极本体论;就太极与阴阳的关系而言,此一体系可称为太极本源论。据朱子在写作讨论《太极解义》过程中与杨子直书,他最初是用太极为体、动静为用来理解太极与动静的关系,但后来放弃了,改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的关系。那就是说,他以前认为,太极是体,动静是太极所发的用,二者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这显然不适合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是本体和载体的关系,把动静作为载体,这就比较适合太极和动静的关系了。本然之妙表示太极既是本体,又是动静的内在原因(动力因),“妙”字就是特别用来处理与动静关系的、用来说明运动根源的,这也是中国哲学长久以来的特点。与《周易》传统以“神”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不同,朱子以“道”即太极作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
“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则明确用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区别太极与阴阳,即太极是形而上的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二者有清楚的分别。把太极明确界定为道,这样就与把太极解释为理,更为接近了。
“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著是显著的用,微是内在深微的体。从微的角度看,太极就是动静阴阳之理,在内在的体;从著的角度看,动静阴阳运行变化不同,是表现著的用。所以,朱子认为太极和动静阴阳还是存在着体用的分别。特别是,这里直接以太极为理,为动静阴阳之理,提出理和动静阴阳始终是结合一起的,强化了理的意义。朱子认为,既不能说从某一个时期开始理和动静阴阳二者才相结合,也不能说将在某一个时期二者将会分离。太极始终是内在于动静和阴阳的。本来,在宇宙论上,动静就是阴阳的动静,但由于《太极图说》讲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地说,动静就成为先在于阴阳、独立于阴阳的了。
第三段,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朱子注: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9]
如果说第二段的解释关注在动静,这一段的解释关注的中心则在阴阳。从太极的动静,导致阴阳的分化与变合;有阴阳的一变一合,则产生了五行的分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这是一套由阴阳五行展开的宇宙生化论。与前面第二段不同,这里对太极的定义不是从动静的枢纽来认识太极,而是从阴阳的所以然根据来认识太极。或者说,前面是从“所以动静者”来认识太极,这里是从“所以阴阳者”界定太极。“所以为阴阳者”的视角就是存在的视角,而不是运动的视角了。至于“太极之本然”,即是《太极图解》的“本体”,“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所以阴阳者”的观念本来自二程,区分“阴阳”和“所以阴阳”,认为前者是形而下者,后者是形而上者,这种思维是朱子从程颐吸取的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对照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和吕祖谦的《太极图义质疑》,可以明显看出朱子此时的哲学思维的优势,这也是何以张、吕对朱子解义的意见只集中在“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一句,而对其太极本体论、太极根源论、太极生化论并未提出意见的原因。
三、“太极”本性论
从第四段开始,由太极动静阴阳论转到太极本性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注:
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10]前面已经说过,宇宙中处处是阴阳,而凡有阴阳处必有所以为阴阳者,这就是“无适而非阴阳”“无适而非太极”。阴阳分化为五行,五行发育为万物,万物中也皆有太极,故说“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各具于事物之中的太极即是事物之性,太极就是“性之本体”,这就转到了万物的本性论。万物因气禀不同而造成“各一其性”,即各异其性、各有各的性,互不相同。“各一其性”是说明万物由气禀不同带来的性的差异性。但朱子同时强调,太极无不具于每一物之中,这才真正体现出“性无所不在”的原理。这样朱子的解释就有两个“性”的概念,一个是“各一其性”的性,一个是“太极之全体”的性,前者是受气禀影响的、现实的、差别的性,后者是不受气禀影响的本然的、本体的、同一的性。故每一个人或物都具备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但这种具备不是部分地具有,而是全体地具有。每一个人或物都具有一太极之全体作为自己的本性。这是朱子对《太极图说》自身思想的一种根本性的发展,即从各一其性说发展为各具太极说。
第五段,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朱子注:
夫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无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所谓“妙合”者也。“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矣。[11]
上段最后讲性无不在,这里接着把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也作为性无不在的证明。这就是说,气质所禀与二五之精相联系,太极本体与无极之真相对应,各一其性与各具太极混融无间,此即性无不在的体现。重要的是,此段明确声明:“‘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这就把无极之真,同时也把太极解释为“理”了,把太极和理贯通,由此打开了南宋理气论哲学的通途。当然,太极也仍被确定为“性”,“性为之主”本是胡宏的思想,这里显示出湖湘学派把太极理解为性对朱子仍有影响。这里的性为之主,也从特定方向呼应了太极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的意义。“以理言”和“以气言”的分析使得理气论正式登上道学思想的舞台。没有《太极解义》,朱子学的理气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哲学论述。
对照《太极图解》可知,太极本性论是朱子《太极解义》的重要思想。朱子强调,男与女虽然各有其性,互不相同,但男与女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男女一太极也”。万物各异其性,而万物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万物一太极也”。尤其是,这里提出了万物各具的太极与宇宙本体的太极的关系,朱子认为,“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是万物的存在总体,其存在的根据是太极,而每一个人或物,也具有此一太极为其本性。每个人或物对宇宙总体而言是分,但每个人或物具有的太极并不是分有了太极的部分,而是全体,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后来朱子在《语类》中反复申明了这个道理。如朱子与张栻书所讨论的,朱子认为“各具一太极”的说法意在强调“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用太极的概念来表达性理学的主张。
四、“全体太极”之道
以下开始转到人生论。
第六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朱子注:
此言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也。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然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而五性之殊,散为万事。盖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圣人全体太极有以定之,则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而违禽兽不远矣。[12]
“全”或“全体”是《太极解义》后半部的重要概念,是属于人生境界与功夫论的概念。朱子认为,人物之生,皆有太极之道,此太极之道即人与物生活、活动的总原则,也是人与物的太极之性的体现。物所禀的气浑浊不清,故不能有心,亦不可能实现太极之道。只有人独得气禀之秀,其心最灵,才有可能使人不失其太极本性,体现天地之心,确立人极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皆能如此,唯有圣人能“全体太极”,即完全体现太极,完全体现太极之道和太极之性,真正确立人极。这也就是下段所说的“定”和“立人极焉”。
第七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注: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而圣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若程子论乾坤动静,而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亦此意尔。[13]
《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开始,以人极为结束,而人极的内涵是中正仁义而主静,中正仁义是基本道德概念,主静是修养方法,以人极而兼有二者,这在儒学史上是少见的。但《荀子》中也谈到静的意义,《礼记》的《乐记》本来强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故“静”在儒学史上也曾受到注意,尤其是《乐记》的思想在宋代道学中很受重视,在这个意义上,主静的提出不能仅看作受到佛道修养的影响。但对朱子和南宋理学而言,必须对主静做出新的论证。
根据六、七两段的朱子注,他提出,众人虽然具动静之理,即具有太极,但常常失之于动,其表现是“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即欲望、情欲的妄动,对私利的追逐,必须以人极“定”之,“定”是对于“失之于动”的矫正,也是使人不至失之于动的根本方法。所以在朱子的解释中,静与定相通,一定要分别的话,可以说静是方法,定还是目的,这就是“于此乎定矣”。
在第六段朱子注强调“不失其性之全”“圣人全体太极”,在第七段,又提到“圣人全动静之德”“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全体”就是全幅体现,是一实践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全动静之德,是特就人对动静之理的体现而言,全动静之德的人,就不会失之于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行事中正仁义,因此全动静之德就是全太极之道,全体太极也就是全体太极之道,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在第七段之后,朱子还说:“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14]我们记得,在《太极图解》中也说过“全乎(太极)之体用也”,这些都是相同的意思。
当然,由于《太极图说》本文强调主静,故朱子也同意“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为什么要本于静、主于静?照朱子说,这是因为“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即是说,静是体,动是用,所以以主静为本。《太极图解》比《太极图说解》这里说得更具体:“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者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极)于是乎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朱子与张栻、吕祖谦做了反复的讨论。此外朱子也指出,主静所指的这种“静”不是专指行为的,而是指心的修养要达到“此心寂然无欲而静”。这当然是合乎周子本人主张的“无欲故静”的。
应当指出,朱子《太极解义》中在论及主静时没有提到程颐的主敬思想,只在一处提及“敬则欲寡而理明”,这对于在己丑之悟已经确认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宗旨的朱子,是一欠缺。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重视程门主敬之法,对朱子是一个重要补充。
五、《太极解义》引起的哲学论辩
朱子《太极解义》文后有《附辩》,其中提到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或谓)和三种次要的反对意见(有谓)。朱子简单叙述了这些意见: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15]
所谓“读者病其分裂已甚”,应是张栻的意见(张栻《寄吕伯恭》)。四个“或谓”中,第一个“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应是廖德明的意见(朱子《答廖子晦一》);第二个“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应是吕祖谦的意见(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第三个“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是吕祖谦的意见(张栻《答吴晦叔》),第四个“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应是张栻的意见(朱子《答张敬夫十三》)。至于“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应该都与张栻、吕祖谦的意见有关。
朱子在《附辩》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回应:
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16]
这是关于阴阳观的讨论,在朱子看来,阴阳变化流行,属于阳动;而成型固定,属于阴静。认为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继之者善和成之者性的分别。所以把继之者善作为阳动,把成之者性作为阴静,这是很自然的。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17]
太极是理,无形无象,阴阳是气,已属形象,二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这是二程哲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朱子完全继承了这一点。特别把道器的分别运用于理气的分析。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18]朱子认为,仁义中正如同元亨利贞,既然在《通书》中元亨属于诚之通,利贞属于诚之复,则四德之中,元亨与利贞之间就有体用之分。同理,中正仁义也就可以有体用之分。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19]
这是朱子用吕祖谦的意思回应张栻的怀疑。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云:“‘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20]朱子吸取了吕氏的这一意见。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21]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张拭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就不是一源了。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理是体,事物是用,一源是言体言理,无间是言用言事;言理体先而用后,言事先用而后体,二者角度不同。所以朱子认为,虽然,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但二者在形而上学上可分为先后。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22]
最后这点较为复杂。照“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的质疑,这是反对把仁归属于阳动,认为仁是包含四德的统体,怎么能把仁只归结为一个特定方面呢?朱子的辩解是,《太极图说》以“仁”配“义”,然后以“仁义”与“中正”相对,这说明《太极图说》中的仁不是专言包四德的仁,从而也就不是“统体”的仁,只是偏言的仁、分别而言的仁。这个仁是义之体,义是仁之质,具有体用的差别。朱子此段回应的对象不甚确定,参与太极解义之辩的人中,只有吕祖谦《答朱侍讲六》提及仁包四德,但所论与这里所说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这几条都和体用问题有关,而张栻颇注重体用之论,吕祖谦也就体用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可见体用问题是太极解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总之,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美〕田浩
在学术思想繁荣发展的12世纪,朱熹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互动使得他最终可以升至经典的权威解读者以及道学群体的领军人物。在宋代,相比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6~2017)先生所使用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指比“理学”更广的范畴,道学的含义要具体得多。但道学要远比陈荣捷(1901~1994)教授所提出的“新儒学”——专指被二程及朱熹所发扬的思想流派——宽泛得多。[1]一些学者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词汇的差异或仅仅关注于道学在1181年后的发展,所以他们或者将“道学”与陈荣捷先生的“新儒学”混为一谈;或者继续将“新儒学”与“理学”这二者假设成等同为一。[2]中国学者经常使用“学派”这一标签来称呼湖湘、浙东之类的地域分支,然而“道学”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范畴。相较于宋代所形成的思想学派而言,这种打着“学派”标签的地域分支常给西方学者一种有更强的凝聚力、高度一致性及范围更广泛的感觉,所以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否定这类地方团体等同于一个学派。
在和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当中,起先是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其后是陈亮(1143~1194)和陆九渊(1139~1193)等人,他们不但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贡献了若干思想概念,而且朱熹在回应他们的观点或立场的过程中,他们也启发或刺激了朱熹更进一步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为了突出朱熹同时代学者的重要性,田浩曾以个案研究对比朱熹早期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及其后来与陈亮、陆九渊的互动,以及朱熹如何在1181年为吕祖谦写的悼词中开始宣称他自己是道学唯一的权威。他在悼词中大声疾呼:“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新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3]1181年之后,朱熹在道学群体中变得更为重要,他有时甚至对其他学者不屑一顾。
朱熹对其同时代儒家的品评影响了宋代以后直至20世纪的学者,因此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重视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甚或将他们描述为与朱熹思想完全敌对的竞争者。在阅读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时,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一个转折点,许多中国学者对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他们进行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蔡方鹿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4],朱汉民、陈谷嘉的《湖湘学派源流》[5],潘富恩、徐余庆的《吕祖谦评传》[6],张立文对陆九渊的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7],徐纪芳则探讨了陆九渊的弟子情况[8]。田浩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对陈亮的思想及其与朱熹的论辩给予了正面积极的重新评价,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观点开始在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此外,他在1992年出版了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His'sAscendancy,即《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其1996年出版了中文版,并于2009年增订《朱熹的思维世界》,论述了与朱熹同时代儒家对朱熹思想观念及道学权威的影响要远比传统观点所承认的要大得多。田浩的著作及其与狄百瑞在《东西方哲学》[9]上的辩论,唤起学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将这些学者一方面视为自身强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视为在道学发展及朱熹思想主流化过程中的关键对话者。因此田浩的论著大致可以代表这一个重大转折,即将朱熹置身于与其同时代学者环境中来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强调朱熹同时代思想家的贡献和他们致力于社会政治的改革与提升道德修养的努力延续了这一转折。比如余英时对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蓝图给予了极大关注。[10]
因此本文以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也简短亮相,帮助传达这些主要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展示朱熹时代儒家团体的分支之内与之间各种思想的消长。虽然许多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没有在20世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相当可观,所以本文只能选取其中一些成果来加以说明。本文介绍学界所涌现的大量相关研究目的在于以此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变。总之,因为共同尊奉儒家经典及北宋主要的儒学家,使得朱熹与同时代的儒学家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
一、张栻与湖湘学派
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即今天的湖南、湖北一带,在公元12世纪变得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外来家族:从福建北部迁来的胡氏家族和四川迁来的张氏家族。胡安国(1074~1138)宣称自己是二程的追随者,奠定了道学湖湘学派的思想基石。此外胡安国还与二程的早期门人杨时(1053~1135)一起编纂了一本记录二程语录的早期版本。胡安国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春秋》的注解,其中强调抵抗“蛮夷”,这一注本后来成为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官方经典注本。胡安国去世之后,宋朝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以保证胡家的经济来源。胡宏的著作《皇王大纪》继续关注国家的历史与政治,这种关注在他的早期作品《知言》中也相当明显。虽然很多学者关注胡宏在《知言》有关“性”的阐发,叶翰教授论证了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不断变化的正统和对外族的征讨等政治议题构成了这部书的主要框架。其书第一章讨论天心与天命,最后一章讨论宋朝被女真占领的“中原”地区。与通常对“体”和“理”的哲学解释不同,胡宏认为这些概念意味着统贯、治理、条理事物的意思。[11]因此他醉心于重建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古代理想模式——井田制,即国家分给家族或宗族土地作为经济或制度的基础。
大多数学者关注《知言》怎么从思想层面来解释“心”和“性”的含义,但这一点遭到朱熹的质疑与谴责。胡宏论及“天命为性,人性为心”12]。又如:“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13]朱熹认为胡宏误解了“性”的含义,而将心和人的情感相混淆。朱熹认为人性的本质就像天理存于人性一样,因此他批评胡宏忽略了人性和天理的重要性。而且,朱熹认为“天理”或“理”内在于人性之中,而胡宏将“理”作为人行为的目标。虽然胡宏对佛学怀有敌意,但朱熹认为胡宏有关“心”和“性”概念源于佛教。[14]尽管如此,胡宏认为自己是道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告诫他的学生:“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5]张栻是胡宏学生并继承他的道学使命,继续修订《知言》,同时他还是主战派领袖宰相张浚(1097~1164)之子。因为有如此非凡的背景,加之他的学识和仕途经历以及他在长沙主讲岳麓书院多年,所以张栻从1164年至1168年成为道学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并不奇怪。他和吕祖谦被认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还曾称赞张栻为“道学之懿,为世醇儒”[16]。
17世纪的中国首部思想史《宋元学案》给张栻以不朽的评价:“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17]基于这个评价,牟宗三(1909~1995)进一步评价认为,相比朱熹和陆九渊,张栻则更接近孟子。牟先生同时指出张栻没有成功地维护程颢和胡宏的孟子传统,也正因为张栻后来认同了朱熹的观点最终导致朱熹的非正统观点成为宋代至20世纪的正统思想。虽然田浩对牟先生有关张栻与程颢两人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湖湘学派衰微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田浩强调张栻生前对朱熹观点的影响,主要是“修身”和“仁”方面。从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对张栻的研究来看,以上观点也得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回应。[18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足以论证这一点:向世陵称赞张拭是湖湘学派的整合者,不过他也认为张栻从来没有对胡宏“性”的观点有所创新,同时在与朱熹争论的过程中张栻还放弃了湖湘学派的特色。[19]李可心则批评张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对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其哲学思想的声音为朱熹的所湮没。此外,张栻关于性与心的观点亦充满矛盾。[20]
张栻有关“心”和“性”的观点,特别是其与孟子、程颢和胡宏的关系实际非常复杂。孟子认为人心本善,程颢则以为人们不能否定恶也是人性。胡宏拓展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性”超越了善与恶,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他认为“性”是绝对的,并且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张栻通过将“人性”等同于万事万物的“理”,进一步发展了胡宏的说法。孟子将(人)性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但是他们从孟子对人性的观点中发展出自己的新观点。同时张栻并不十分认同胡宏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这也表明张栻更倾向于孟子的观点。尽管如此,孟子认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人性中比“四德”(即“仁”“义”“礼”“智”)更为基本。张栻认为“德”是人性之未发,但其已发属于心。张栻将“德”的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但其已发状态则与心联系,因此,与孟子不同,他在人性与心之间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张栻断定人性包含着所有的“理”或准则,他也表示理和心两者并无差异,没有必要将两者相整合,朱熹则否认两者是一致的。张栻曾谈及:“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21]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他认为理和心几无二致,但张栻反对将心简单地看作理。此外,他除了将“恶”解释为人的身体与其他事物互动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张栻还通过描述利与义之间的矛盾斗争进而将人欲与天理相对立。这种人性和天理之间对立性的矛盾冲突使其与“二程”中程颐的理论更加相近。[22]
近年以来,相关研究日益细致深入,尤其是有关张栻对“性”和“太极”的研究。2015年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张栻研究研讨会中所收录的论文正反映了张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3]比如其中一些论文涉及从张栻对经典的解释——尤其在《易经》和《诗经》方面——到他的礼制思想及他的教育观点与当今教育的关联等诸方面。2017年11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纪念“朱张会讲”八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分发《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4]。总而言之,近些年有关张栻的研究十分活跃,他对道学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了更加广泛的认可。
数百年以来,有关张栻思想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他对朱熹思想的影响,而非其本身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关于他在修身方面的观点。儒家经典《中庸》强调的是在情感被激发之前,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恰当的程度进而达到的一种均衡、和谐的状态。[25]程颐提高了修身的要求,他要求弟子保存和守护这种感觉,就像他们在心中被唤起一样,并在心被表达之后,检验这种感觉。身处湖湘的张栻师法胡宏,认为“性”和“心”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他主张在行动中拓展认识,而不是关注于静坐和修身中提高涵养。[26]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受到杨时的影响,杨时在福建以二程学说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学说,主张在感觉被唤起前静坐冥想,不过朱熹对杨时的方法有所不满。因为仰慕张栻的学问,朱熹在1167年前往岳麓书院与其论学。两人当面论学,张栻说服朱熹将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将已发状态与“心”相关联。朱熹回到福建之后,给张栻的四封信表明他接受了张栻的这一观点,但不久之后,朱熹就声明这四封信中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抱怨放弃了杨时静修沉思的方法后,自己在道德要求上有所下降。1169年他写信给张栻,宣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心的“体用”(实质和功能)。1172年他在《中和旧说》中的序言中,阐明了他思想的变化,以及怎样达到他所认为的正确中和观点的历程。[27]这一变化的取得一方面由于朱熹对闽学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在于他不但得益于湖湘学者的启发,而且还超越了湖湘学派,这标志着朱熹自信在思想的成熟和自己于道学中的权威方面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朱熹称张栻接受了这一新的思想体系,但是很难找到张栻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文献记载,因为朱熹在编纂张栻的文集时,并没有将张栻所有的书信和著作纳入其中。[28]
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同样也难以判断,他们有关重新解释“仁”一系列的讨论,试图纠正“仁”说陷于一偏的观点,特别是“二程”及其门人忽略“仁之爱”,过分地强调“仁之理”。几个世纪以来,朱熹对“仁”的终极定义——“爱之理”和“心之德”——一直为人所称道。相当一部分传统的和20世纪的学者断言张栻折服于朱熹的观点,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张栻最后完成的文章实际出自朱熹之手。[29尽管如此,刘述先(1934~2016)先生和田浩指出朱熹在其后与吕祖谦弟弟吕祖俭的书信中声明“心之德”的提法是张栻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起初遭到了朱熹的拒绝。[30]更重要的发现则源于陈来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张栻的《张子太极解义》,这本书说明了张拭在提升周敦颐(1017~1073)在道学中地位的重要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周敦颐地位的抬升一般被想当然地归于朱熹的功劳。[31]这些新的发现表明,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而言,近些年学界在张栻对朱熹的影响这一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二、吕祖谦与浙东学派
浙东(今属浙江)儒者与湖湘地区的儒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二程道学的两大分支——胡氏家族与吕氏家族之间的友谊。张九成(1092~1159)是联结这两个地区的另外一个纽带,他的心学观念对胡氏及吕氏家族皆有影响。[32]此外浙东与湖湘儒者都有着对国家强烈的使命感,而且他们都极力主张赶走占领中原腹地的女真人。因为吕氏家族从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末涌现了许多达官显贵和知名学者,这种家族的光环对吕祖谦的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带着吕氏家族对宋王朝的忠诚和乐观,他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编纂史学、制度方面的著作,以求更好地理解和改进治国之道。
吕氏家族长期以来以其博学,即精通中原文献而闻名,同时并不局限于师承一家的狭隘学派思想。就像蒋伟胜认为,吕家中原文献的藏书注重北宋特别是“二程”及张载(1020~1077)的著作,这也成为吕祖谦思想的核心观点。[33]因此吕祖谦非常自然地表达他治学方法(被牟宗三总结为“一元”论,被马恺之称为“有机”)[34]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将经典和历史、修身、政治及制度活动相结合。[35]他对道学早期思想家的贡献持认可态度,并试图保存他们著作的原貌,所以他曾批评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评点。[36]在此之前,他还为了维护胡宏的原本而反对朱熹修订、改变胡宏的《知言》。基于程颢、张九成、张栻对“心”的强调,吕祖谦直接通过“理”来分析“心”。与此相反朱熹关注程颐的“性即理”来建立他有关人性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心即是理。朱熹倾向把天理和人欲视作互相敌对的二元,吕祖谦认为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人的情感会寻求和谐甚至互相融合。因此吕祖谦在修身方法上更加倾向于张栻,即在行动中审视自己的实践,而不是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先冥想而后再实践。
吕祖谦认为修身应更多地在现实世界多加实践并学习“实学”,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浙东儒学一大特征。这种实学也运用了这样的口号“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和“切用于世”[37]。因为吕祖谦思想当中修身和实学互相融合,正如事功学、功利学说与朱熹的道学学说有某些互通之处一样,所以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38]
吕祖谦和朱熹主要的合作在于书院教育方面。田浩曾强调他们两人对书院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论及吕祖谦对朱熹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在朱熹从事书院教学之前,吕祖谦就有大量的门生,还有怎样发展书院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吕祖谦帮助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还为这座著名的宋代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朱熹为他的学生制定治学方向,并通过书院教学来提升其在经典解读及道学正统方面的权威地位,后来朱熹在这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在书院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快使其故去的友人黯然失色。
因为致力于治国之道的研究,吕祖谦将其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研究古代和当时历史的演变,以求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从中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比如他曾告诫学生应该从历史中观察事物如何变化,而不是将历史只看作记忆中的大量历史事件。吕祖谦还对其门生提到,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该先停下来设身处地地考虑,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39]吕祖谦的许多史学著作是在讲学的同时完成的,比如他所作的《东莱博议》是为了指导学生如何在科举考试中写策论,可惜的是他的《大事记》只编到了公元前90年,在他病重直到去世前他都努力接续《左传》这一记录历史的传统。他的史学著作特别关注制度的发展,比如他的《历代制度详说》辑录了历代制度方面的史料。
吕祖谦和朱熹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些主要区别。朱熹特别注重经的地位,吕祖谦则认为经与史同等重要。同时他们两人都认为上古三代才是黄金时代,朱熹将天理和修身之道作为思想的准则,但吕祖谦更关注制度所产生的历史效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关注道德问题,吕祖谦则更注重制度因素。在评论历史学家方面,朱熹首先看他们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则较少关注史学家的个性,而是注重用历史来解释历史。朱熹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历史,而吕祖谦将天理融入到历史当中。[40]
在西方学界,马恺之(Kai Marchal)教授对吕祖谦的政治思想及其与朱熹的关系有最深入的研究。这两位道学家都认为通过个人修身进德提升儒家道德理想,进而可以从根本上促成社会和国家的变革。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的道德楷模中,特别是从孟子及北宋儒家那里继承了自信。虽然两人都取法于儒家经典,相对于朱熹而言,吕祖谦更加主张儒家激进的政治改革。因此相较于吕祖谦而言,朱熹倾向于远离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而更倾向于提高个人及群体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在其最后两年对政治上的挫败感到失望,所以如果他能像朱熹一样长寿的话,他对儒家道德能在根本上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观点也许也会有所动摇。尽管如此,有关儒家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主张成为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点。[41]这些分歧无疑反映了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然而这些也是他们两人思想差异的反映。
比如吕祖谦对王安石(1021~1086)的评价就比朱熹要积极得多,如他认为王安石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虽然吕祖谦也批评了王安石,但吕祖谦表达了一个和王安石相同的目标,马恺之总结为:“通过大规模的重组国家机构以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有为的政府以应对社会和政治上的挑战。”[42]吕祖谦对制度和史学的研究不但为改革提供了具体的理念和制度,还使他比道学阵营中大多数试图通过《周礼》中理想化的描述来恢复周朝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更加务实。比如在公元780年杨炎“两税法”的推行消除了在市场上购买土地的障碍后,恢复“井田制”的目标变得日益渺茫。但吕祖谦仍然很有信心,相信通过实际努力重建宗族谱系、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在社会上恢复由来已久的秩序和儒学家庭伦理。比如他曾写到虽然全面复兴古代制度风俗十分困难,但也有可能通过限制私有财产和保留地方武装开始逐步恢复。
马恺之也反驳一些现代学者对吕祖谦的批评,同时这也是对朱熹批评吕祖谦博杂和对最基本的道德概念关注不够的回应。比如朱熹同意一位门人对吕祖谦的描述:“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43]田浩曾指出朱熹对吕祖谦怀有敌意的批评几乎都始于这位好朋友去世之后。在和陈亮以及其他浙东儒者论辩的时候,朱熹认为这是吕祖谦错误的延续。[44]中国现在也有学者指出朱熹后来尖锐批评吕祖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追求道学权威并努力限制浙东学派的影响力。[45]
与包弼德教授将吕祖谦描述为“搞分门别类的书生”[46]不同,马恺之举例说明吕祖谦将自我修身与历史中的真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吕祖谦的许多研究关注探讨自我修身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了尽到士大夫的责任进而影响国家统治,他试图说服皇帝恢复传统的官僚集团以此作为对皇帝行为的制衡。但朱熹试图说服皇帝自愿限制自己的权力,吕祖谦则认识到通过制度限制皇权的必要性。皇权倾向于朱熹而非吕祖谦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朱熹主张关注皇帝内心道德的转变相比,吕祖谦通过制度来限制皇帝行为的方法看起来不合礼法并具有敌意。因此“与其他儒者思想家相比,吕祖谦较早地意识到‘道德的内化’的政治结果”[47]。
魏希德教授也曾对吕祖谦在1168年至1181年期间的道学领导地位提出质疑,她指出为什么吕祖谦没有像朱熹一样经常使用“道学”这一概念?[48]虽然他们在许多方面互相认同或合作,但我们应该了解他们两人的差别。除了其博学和善于综合各种治学方法外,吕祖谦比朱熹更早认识到道学群体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吕祖谦反映作为道学早期的社会政治联盟,其政治理想使得他们能够容忍相当多元的儒家思想。与此相反,朱熹特别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教化或思想的目的,所以他在使用“道学”来论述他的议题时要比吕祖谦更为严格。在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的密切关注反映了他对“醇儒”的认识,并努力清除道学内部被其他思想所影响的人。作为经典和传统的诠释者,朱熹重点关注思想的纯粹性及自己的权威地位,因此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探索思想意识纯粹性的过程中,朱熹较经常使用“道学”或“道统”等术语。朱熹的这种探索不但在其1181年对吕祖谦的悼词中宣称自己在道学中的领导地位中有所表现,而且在此后十年中他面对陈亮和陆九渊的挑战时显露无遗。
总之,虽然20世纪学者大多忽略了吕祖谦,但自从1992年开始学界在此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力地支持了田浩对吕祖谦在1168年到1181年之间是最重要思想家的评价。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吕祖谦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以及“主盟斯文”,他也是社会的精英、史学家和士大夫[49];二是他建立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基础,特别将心的修养与研究历史和经典相结合[50;三是他的博学并没有削弱他和张载及二程的思想渊源,此外他投身于修身[51];四是他作为道学家领袖并不受师承或某个派别的限制[52;五是吕祖谦对朱熹的重要影响在于其对经典的认识、书院教学和编纂《近思录》等,在宋代以后他对浙东地区的儒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53]
三、结语
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并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世纪和当代学者肯定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观念和贡献的一大因素在于地域的认同,不过将这种转变仅仅归为地域的认同未免过于片面。虽然除了直接驳斥其论点,中国学者鲜少提到外国学者的著述,但他们隐含地分享田浩的观点,也对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投以更多的关注。
本文是我参与撰写的由香港中文大学黄勇、吴启超两位教授主编的《朱熹哲学的指南》(The 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一书第十二章《朱熹与其同时代的儒家》(Zhu Xi's Contemporaries)的一部分。我之所以献上此文是因为一些参加岳麓书院会议的同人们也许会对这样一个面向西方公众的概述的例子感兴趣。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从与2016~2017年度来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的两位学者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玉敏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任仁仁及普渡大学历史系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的讨论中受益良多。任仁仁还为本次会议特将中文稿译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殷慧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帮忙修改译稿。在此谨向他们略表谢忱。
16]
这是关于阴阳观的讨论,在朱子看来,阴阳变化流行,属于阳动;而成型固定,属于阴静。认为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继之者善和成之者性的分别。所以把继之者善作为阳动,把成之者性作为阴静,这是很自然的。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17]
太极是理,无形无象,阴阳是气,已属形象,二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这是二程哲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朱子完全继承了这一点。特别把道器的分别运用于理气的分析。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18]朱子认为,仁义中正如同元亨利贞,既然在《通书》中元亨属于诚之通,利贞属于诚之复,则四德之中,元亨与利贞之间就有体用之分。同理,中正仁义也就可以有体用之分。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19]
这是朱子用吕祖谦的意思回应张栻的怀疑。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云:“‘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20]朱子吸取了吕氏的这一意见。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21]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张拭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就不是一源了。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理是体,事物是用,一源是言体言理,无间是言用言事;言理体先而用后,言事先用而后体,二者角度不同。所以朱子认为,虽然,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但二者在形而上学上可分为先后。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22]
最后这点较为复杂。照“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的质疑,这是反对把仁归属于阳动,认为仁是包含四德的统体,怎么能把仁只归结为一个特定方面呢?朱子的辩解是,《太极图说》以“仁”配“义”,然后以“仁义”与“中正”相对,这说明《太极图说》中的仁不是专言包四德的仁,从而也就不是“统体”的仁,只是偏言的仁、分别而言的仁。这个仁是义之体,义是仁之质,具有体用的差别。朱子此段回应的对象不甚确定,参与太极解义之辩的人中,只有吕祖谦《答朱侍讲六》提及仁包四德,但所论与这里所说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这几条都和体用问题有关,而张栻颇注重体用之论,吕祖谦也就体用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可见体用问题是太极解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总之,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美〕田浩
在学术思想繁荣发展的12世纪,朱熹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互动使得他最终可以升至经典的权威解读者以及道学群体的领军人物。在宋代,相比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6~2017)先生所使用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指比“理学”更广的范畴,道学的含义要具体得多。但道学要远比陈荣捷(1901~1994)教授所提出的“新儒学”——专指被二程及朱熹所发扬的思想流派——宽泛得多。[1]一些学者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词汇的差异或仅仅关注于道学在1181年后的发展,所以他们或者将“道学”与陈荣捷先生的“新儒学”混为一谈;或者继续将“新儒学”与“理学”这二者假设成等同为一。[2]中国学者经常使用“学派”这一标签来称呼湖湘、浙东之类的地域分支,然而“道学”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范畴。相较于宋代所形成的思想学派而言,这种打着“学派”标签的地域分支常给西方学者一种有更强的凝聚力、高度一致性及范围更广泛的感觉,所以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否定这类地方团体等同于一个学派。
在和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当中,起先是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其后是陈亮(1143~1194)和陆九渊(1139~1193)等人,他们不但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贡献了若干思想概念,而且朱熹在回应他们的观点或立场的过程中,他们也启发或刺激了朱熹更进一步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为了突出朱熹同时代学者的重要性,田浩曾以个案研究对比朱熹早期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及其后来与陈亮、陆九渊的互动,以及朱熹如何在1181年为吕祖谦写的悼词中开始宣称他自己是道学唯一的权威。他在悼词中大声疾呼:“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新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3]1181年之后,朱熹在道学群体中变得更为重要,他有时甚至对其他学者不屑一顾。
朱熹对其同时代儒家的品评影响了宋代以后直至20世纪的学者,因此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重视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甚或将他们描述为与朱熹思想完全敌对的竞争者。在阅读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时,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一个转折点,许多中国学者对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他们进行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蔡方鹿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4],朱汉民、陈谷嘉的《湖湘学派源流》[5],潘富恩、徐余庆的《吕祖谦评传》[6],张立文对陆九渊的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7],徐纪芳则探讨了陆九渊的弟子情况[8]。田浩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对陈亮的思想及其与朱熹的论辩给予了正面积极的重新评价,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观点开始在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此外,他在1992年出版了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His'sAscendancy,即《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其1996年出版了中文版,并于2009年增订《朱熹的思维世界》,论述了与朱熹同时代儒家对朱熹思想观念及道学权威的影响要远比传统观点所承认的要大得多。田浩的著作及其与狄百瑞在《东西方哲学》[9]上的辩论,唤起学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将这些学者一方面视为自身强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视为在道学发展及朱熹思想主流化过程中的关键对话者。因此田浩的论著大致可以代表这一个重大转折,即将朱熹置身于与其同时代学者环境中来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强调朱熹同时代思想家的贡献和他们致力于社会政治的改革与提升道德修养的努力延续了这一转折。比如余英时对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蓝图给予了极大关注。[10]
因此本文以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也简短亮相,帮助传达这些主要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展示朱熹时代儒家团体的分支之内与之间各种思想的消长。虽然许多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没有在20世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相当可观,所以本文只能选取其中一些成果来加以说明。本文介绍学界所涌现的大量相关研究目的在于以此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变。总之,因为共同尊奉儒家经典及北宋主要的儒学家,使得朱熹与同时代的儒学家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
一、张栻与湖湘学派
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即今天的湖南、湖北一带,在公元12世纪变得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外来家族:从福建北部迁来的胡氏家族和四川迁来的张氏家族。胡安国(1074~1138)宣称自己是二程的追随者,奠定了道学湖湘学派的思想基石。此外胡安国还与二程的早期门人杨时(1053~1135)一起编纂了一本记录二程语录的早期版本。胡安国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春秋》的注解,其中强调抵抗“蛮夷”,这一注本后来成为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官方经典注本。胡安国去世之后,宋朝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以保证胡家的经济来源。胡宏的著作《皇王大纪》继续关注国家的历史与政治,这种关注在他的早期作品《知言》中也相当明显。虽然很多学者关注胡宏在《知言》有关“性”的阐发,叶翰教授论证了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不断变化的正统和对外族的征讨等政治议题构成了这部书的主要框架。其书第一章讨论天心与天命,最后一章讨论宋朝被女真占领的“中原”地区。与通常对“体”和“理”的哲学解释不同,胡宏认为这些概念意味着统贯、治理、条理事物的意思。[11]因此他醉心于重建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古代理想模式——井田制,即国家分给家族或宗族土地作为经济或制度的基础。
大多数学者关注《知言》怎么从思想层面来解释“心”和“性”的含义,但这一点遭到朱熹的质疑与谴责。胡宏论及“天命为性,人性为心”12]。又如:“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13]朱熹认为胡宏误解了“性”的含义,而将心和人的情感相混淆。朱熹认为人性的本质就像天理存于人性一样,因此他批评胡宏忽略了人性和天理的重要性。而且,朱熹认为“天理”或“理”内在于人性之中,而胡宏将“理”作为人行为的目标。虽然胡宏对佛学怀有敌意,但朱熹认为胡宏有关“心”和“性”概念源于佛教。[14]尽管如此,胡宏认为自己是道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告诫他的学生:“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5]张栻是胡宏学生并继承他的道学使命,继续修订《知言》,同时他还是主战派领袖宰相张浚(1097~1164)之子。因为有如此非凡的背景,加之他的学识和仕途经历以及他在长沙主讲岳麓书院多年,所以张栻从1164年至1168年成为道学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并不奇怪。他和吕祖谦被认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还曾称赞张栻为“道学之懿,为世醇儒”[16]。
17世纪的中国首部思想史《宋元学案》给张栻以不朽的评价:“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17]基于这个评价,牟宗三(1909~1995)进一步评价认为,相比朱熹和陆九渊,张栻则更接近孟子。牟先生同时指出张栻没有成功地维护程颢和胡宏的孟子传统,也正因为张栻后来认同了朱熹的观点最终导致朱熹的非正统观点成为宋代至20世纪的正统思想。虽然田浩对牟先生有关张栻与程颢两人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湖湘学派衰微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田浩强调张栻生前对朱熹观点的影响,主要是“修身”和“仁”方面。从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对张栻的研究来看,以上观点也得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回应。[18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足以论证这一点:向世陵称赞张拭是湖湘学派的整合者,不过他也认为张栻从来没有对胡宏“性”的观点有所创新,同时在与朱熹争论的过程中张栻还放弃了湖湘学派的特色。[19]李可心则批评张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对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其哲学思想的声音为朱熹的所湮没。此外,张栻关于性与心的观点亦充满矛盾。[20]
张栻有关“心”和“性”的观点,特别是其与孟子、程颢和胡宏的关系实际非常复杂。孟子认为人心本善,程颢则以为人们不能否定恶也是人性。胡宏拓展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性”超越了善与恶,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他认为“性”是绝对的,并且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张栻通过将“人性”等同于万事万物的“理”,进一步发展了胡宏的说法。孟子将(人)性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但是他们从孟子对人性的观点中发展出自己的新观点。同时张栻并不十分认同胡宏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这也表明张栻更倾向于孟子的观点。尽管如此,孟子认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人性中比“四德”(即“仁”“义”“礼”“智”)更为基本。张栻认为“德”是人性之未发,但其已发属于心。张栻将“德”的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但其已发状态则与心联系,因此,与孟子不同,他在人性与心之间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张栻断定人性包含着所有的“理”或准则,他也表示理和心两者并无差异,没有必要将两者相整合,朱熹则否认两者是一致的。张栻曾谈及:“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21]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他认为理和心几无二致,但张栻反对将心简单地看作理。此外,他除了将“恶”解释为人的身体与其他事物互动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张栻还通过描述利与义之间的矛盾斗争进而将人欲与天理相对立。这种人性和天理之间对立性的矛盾冲突使其与“二程”中程颐的理论更加相近。[22]
近年以来,相关研究日益细致深入,尤其是有关张栻对“性”和“太极”的研究。2015年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张栻研究研讨会中所收录的论文正反映了张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3]比如其中一些论文涉及从张栻对经典的解释——尤其在《易经》和《诗经》方面——到他的礼制思想及他的教育观点与当今教育的关联等诸方面。2017年11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纪念“朱张会讲”八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分发《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4]。总而言之,近些年有关张栻的研究十分活跃,他对道学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了更加广泛的认可。
数百年以来,有关张栻思想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他对朱熹思想的影响,而非其本身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关于他在修身方面的观点。儒家经典《中庸》强调的是在情感被激发之前,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恰当的程度进而达到的一种均衡、和谐的状态。[25]程颐提高了修身的要求,他要求弟子保存和守护这种感觉,就像他们在心中被唤起一样,并在心被表达之后,检验这种感觉。身处湖湘的张栻师法胡宏,认为“性”和“心”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他主张在行动中拓展认识,而不是关注于静坐和修身中提高涵养。[26]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受到杨时的影响,杨时在福建以二程学说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学说,主张在感觉被唤起前静坐冥想,不过朱熹对杨时的方法有所不满。因为仰慕张栻的学问,朱熹在1167年前往岳麓书院与其论学。两人当面论学,张栻说服朱熹将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将已发状态与“心”相关联。朱熹回到福建之后,给张栻的四封信表明他接受了张栻的这一观点,但不久之后,朱熹就声明这四封信中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抱怨放弃了杨时静修沉思的方法后,自己在道德要求上有所下降。1169年他写信给张栻,宣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心的“体用”(实质和功能)。1172年他在《中和旧说》中的序言中,阐明了他思想的变化,以及怎样达到他所认为的正确中和观点的历程。[27]这一变化的取得一方面由于朱熹对闽学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在于他不但得益于湖湘学者的启发,而且还超越了湖湘学派,这标志着朱熹自信在思想的成熟和自己于道学中的权威方面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朱熹称张栻接受了这一新的思想体系,但是很难找到张栻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文献记载,因为朱熹在编纂张栻的文集时,并没有将张栻所有的书信和著作纳入其中。[28]
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同样也难以判断,他们有关重新解释“仁”一系列的讨论,试图纠正“仁”说陷于一偏的观点,特别是“二程”及其门人忽略“仁之爱”,过分地强调“仁之理”。几个世纪以来,朱熹对“仁”的终极定义——“爱之理”和“心之德”——一直为人所称道。相当一部分传统的和20世纪的学者断言张栻折服于朱熹的观点,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张栻最后完成的文章实际出自朱熹之手。[29尽管如此,刘述先(1934~2016)先生和田浩指出朱熹在其后与吕祖谦弟弟吕祖俭的书信中声明“心之德”的提法是张栻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起初遭到了朱熹的拒绝。[30]更重要的发现则源于陈来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张栻的《张子太极解义》,这本书说明了张拭在提升周敦颐(1017~1073)在道学中地位的重要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周敦颐地位的抬升一般被想当然地归于朱熹的功劳。[31]这些新的发现表明,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而言,近些年学界在张栻对朱熹的影响这一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二、吕祖谦与浙东学派
浙东(今属浙江)儒者与湖湘地区的儒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二程道学的两大分支——胡氏家族与吕氏家族之间的友谊。张九成(1092~1159)是联结这两个地区的另外一个纽带,他的心学观念对胡氏及吕氏家族皆有影响。[32]此外浙东与湖湘儒者都有着对国家强烈的使命感,而且他们都极力主张赶走占领中原腹地的女真人。因为吕氏家族从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末涌现了许多达官显贵和知名学者,这种家族的光环对吕祖谦的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带着吕氏家族对宋王朝的忠诚和乐观,他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编纂史学、制度方面的著作,以求更好地理解和改进治国之道。
吕氏家族长期以来以其博学,即精通中原文献而闻名,同时并不局限于师承一家的狭隘学派思想。就像蒋伟胜认为,吕家中原文献的藏书注重北宋特别是“二程”及张载(1020~1077)的著作,这也成为吕祖谦思想的核心观点。[33]因此吕祖谦非常自然地表达他治学方法(被牟宗三总结为“一元”论,被马恺之称为“有机”)[34]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将经典和历史、修身、政治及制度活动相结合。[35]他对道学早期思想家的贡献持认可态度,并试图保存他们著作的原貌,所以他曾批评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评点。[36]在此之前,他还为了维护胡宏的原本而反对朱熹修订、改变胡宏的《知言》。基于程颢、张九成、张栻对“心”的强调,吕祖谦直接通过“理”来分析“心”。与此相反朱熹关注程颐的“性即理”来建立他有关人性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心即是理。朱熹倾向把天理和人欲视作互相敌对的二元,吕祖谦认为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人的情感会寻求和谐甚至互相融合。因此吕祖谦在修身方法上更加倾向于张栻,即在行动中审视自己的实践,而不是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先冥想而后再实践。
吕祖谦认为修身应更多地在现实世界多加实践并学习“实学”,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浙东儒学一大特征。这种实学也运用了这样的口号“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和“切用于世”[37]。因为吕祖谦思想当中修身和实学互相融合,正如事功学、功利学说与朱熹的道学学说有某些互通之处一样,所以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38]
吕祖谦和朱熹主要的合作在于书院教育方面。田浩曾强调他们两人对书院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论及吕祖谦对朱熹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在朱熹从事书院教学之前,吕祖谦就有大量的门生,还有怎样发展书院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吕祖谦帮助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还为这座著名的宋代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朱熹为他的学生制定治学方向,并通过书院教学来提升其在经典解读及道学正统方面的权威地位,后来朱熹在这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在书院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快使其故去的友人黯然失色。
因为致力于治国之道的研究,吕祖谦将其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研究古代和当时历史的演变,以求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从中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比如他曾告诫学生应该从历史中观察事物如何变化,而不是将历史只看作记忆中的大量历史事件。吕祖谦还对其门生提到,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该先停下来设身处地地考虑,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39]吕祖谦的许多史学著作是在讲学的同时完成的,比如他所作的《东莱博议》是为了指导学生如何在科举考试中写策论,可惜的是他的《大事记》只编到了公元前90年,在他病重直到去世前他都努力接续《左传》这一记录历史的传统。他的史学著作特别关注制度的发展,比如他的《历代制度详说》辑录了历代制度方面的史料。
吕祖谦和朱熹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些主要区别。朱熹特别注重经的地位,吕祖谦则认为经与史同等重要。同时他们两人都认为上古三代才是黄金时代,朱熹将天理和修身之道作为思想的准则,但吕祖谦更关注制度所产生的历史效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关注道德问题,吕祖谦则更注重制度因素。在评论历史学家方面,朱熹首先看他们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则较少关注史学家的个性,而是注重用历史来解释历史。朱熹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历史,而吕祖谦将天理融入到历史当中。[40]
在西方学界,马恺之(Kai Marchal)教授对吕祖谦的政治思想及其与朱熹的关系有最深入的研究。这两位道学家都认为通过个人修身进德提升儒家道德理想,进而可以从根本上促成社会和国家的变革。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的道德楷模中,特别是从孟子及北宋儒家那里继承了自信。虽然两人都取法于儒家经典,相对于朱熹而言,吕祖谦更加主张儒家激进的政治改革。因此相较于吕祖谦而言,朱熹倾向于远离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而更倾向于提高个人及群体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在其最后两年对政治上的挫败感到失望,所以如果他能像朱熹一样长寿的话,他对儒家道德能在根本上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观点也许也会有所动摇。尽管如此,有关儒家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主张成为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点。[41]这些分歧无疑反映了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然而这些也是他们两人思想差异的反映。
比如吕祖谦对王安石(1021~1086)的评价就比朱熹要积极得多,如他认为王安石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虽然吕祖谦也批评了王安石,但吕祖谦表达了一个和王安石相同的目标,马恺之总结为:“通过大规模的重组国家机构以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有为的政府以应对社会和政治上的挑战。”[42]吕祖谦对制度和史学的研究不但为改革提供了具体的理念和制度,还使他比道学阵营中大多数试图通过《周礼》中理想化的描述来恢复周朝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更加务实。比如在公元780年杨炎“两税法”的推行消除了在市场上购买土地的障碍后,恢复“井田制”的目标变得日益渺茫。但吕祖谦仍然很有信心,相信通过实际努力重建宗族谱系、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在社会上恢复由来已久的秩序和儒学家庭伦理。比如他曾写到虽然全面复兴古代制度风俗十分困难,但也有可能通过限制私有财产和保留地方武装开始逐步恢复。
马恺之也反驳一些现代学者对吕祖谦的批评,同时这也是对朱熹批评吕祖谦博杂和对最基本的道德概念关注不够的回应。比如朱熹同意一位门人对吕祖谦的描述:“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43]田浩曾指出朱熹对吕祖谦怀有敌意的批评几乎都始于这位好朋友去世之后。在和陈亮以及其他浙东儒者论辩的时候,朱熹认为这是吕祖谦错误的延续。[44]中国现在也有学者指出朱熹后来尖锐批评吕祖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追求道学权威并努力限制浙东学派的影响力。[45]
与包弼德教授将吕祖谦描述为“搞分门别类的书生”[46]不同,马恺之举例说明吕祖谦将自我修身与历史中的真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吕祖谦的许多研究关注探讨自我修身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了尽到士大夫的责任进而影响国家统治,他试图说服皇帝恢复传统的官僚集团以此作为对皇帝行为的制衡。但朱熹试图说服皇帝自愿限制自己的权力,吕祖谦则认识到通过制度限制皇权的必要性。皇权倾向于朱熹而非吕祖谦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朱熹主张关注皇帝内心道德的转变相比,吕祖谦通过制度来限制皇帝行为的方法看起来不合礼法并具有敌意。因此“与其他儒者思想家相比,吕祖谦较早地意识到‘道德的内化’的政治结果”[47]。
魏希德教授也曾对吕祖谦在1168年至1181年期间的道学领导地位提出质疑,她指出为什么吕祖谦没有像朱熹一样经常使用“道学”这一概念?[48]虽然他们在许多方面互相认同或合作,但我们应该了解他们两人的差别。除了其博学和善于综合各种治学方法外,吕祖谦比朱熹更早认识到道学群体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吕祖谦反映作为道学早期的社会政治联盟,其政治理想使得他们能够容忍相当多元的儒家思想。与此相反,朱熹特别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教化或思想的目的,所以他在使用“道学”来论述他的议题时要比吕祖谦更为严格。在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的密切关注反映了他对“醇儒”的认识,并努力清除道学内部被其他思想所影响的人。作为经典和传统的诠释者,朱熹重点关注思想的纯粹性及自己的权威地位,因此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探索思想意识纯粹性的过程中,朱熹较经常使用“道学”或“道统”等术语。朱熹的这种探索不但在其1181年对吕祖谦的悼词中宣称自己在道学中的领导地位中有所表现,而且在此后十年中他面对陈亮和陆九渊的挑战时显露无遗。
总之,虽然20世纪学者大多忽略了吕祖谦,但自从1992年开始学界在此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力地支持了田浩对吕祖谦在1168年到1181年之间是最重要思想家的评价。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吕祖谦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以及“主盟斯文”,他也是社会的精英、史学家和士大夫[49];二是他建立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基础,特别将心的修养与研究历史和经典相结合[50;三是他的博学并没有削弱他和张载及二程的思想渊源,此外他投身于修身[51];四是他作为道学家领袖并不受师承或某个派别的限制[52;五是吕祖谦对朱熹的重要影响在于其对经典的认识、书院教学和编纂《近思录》等,在宋代以后他对浙东地区的儒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53]
三、结语
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并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世纪和当代学者肯定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观念和贡献的一大因素在于地域的认同,不过将这种转变仅仅归为地域的认同未免过于片面。虽然除了直接驳斥其论点,中国学者鲜少提到外国学者的著述,但他们隐含地分享田浩的观点,也对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投以更多的关注。
本文是我参与撰写的由香港中文大学黄勇、吴启超两位教授主编的《朱熹哲学的指南》(The 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一书第十二章《朱熹与其同时代的儒家》(Zhu Xi's Contemporaries)的一部分。我之所以献上此文是因为一些参加岳麓书院会议的同人们也许会对这样一个面向西方公众的概述的例子感兴趣。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从与2016~2017年度来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的两位学者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玉敏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任仁仁及普渡大学历史系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的讨论中受益良多。任仁仁还为本次会议特将中文稿译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殷慧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帮忙修改译稿。在此谨向他们略表谢忱。
陈来
朱子于乾道己丑(1169)春中和之悟后,在将中和之悟报告张栻等湖南诸公的同时,即开始了他的哲学建构。当年六月他刊行了建安本《太极通书》,接着写作《太极图解》和《太极图说解》,二者合称《太极解义》。次年春,《太极解义》完成,他立即寄给当时在严州的张栻和吕祖谦,此后数年在与张、吕的讨论中不断修改,至乾道癸巳年(1173)定稿。
一、“太极”本体论
让我们先来看《太极图解》。由于图解的图形不易印刷,我们这里把代表太极、阴阳的图形直接转为概念,使文句明白通贯,便于讨论。
对于太极图最上面的第一圆圈,朱子注:
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1]
这是说第一圆圈就是指代《太极图说》的首句“无极而太极”,而落实在“太极”,因为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指“无形无象的太极”。朱子解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即把“本体”作为道学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这一“本体”概念在图解中反复出现,成为《太极图解》哲学建构的突出特点。这也是二程以来道学所不曾有过的。照朱子的解释,太极是动静阴阳的本体,此一本体乃是动静阴阳之所以然的根据和动力因。而这一作为本体的太极并不是离开阴阳的独立存在者,它即阴阳而不杂乎阴阳。“即阴阳”就是不离乎阴阳,“不杂乎阴阳”说明太极并不是阴阳,也不是与阴阳混合不分。这一“不离不杂”的说法开启了朱子学理解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存在关系模式。
对于太极图的第二圆圈,就是所谓坎离相抱图,他认为左半边是阳之动,右半边代表阴之静,而包围在中间的小圆圈则是太极。他指出,太极“其本体也”,意味太极是阳动阴静的本体;又说,阳之动,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阴之静,是“太极之体所以立也”。这就区分了太极的体和用,认为阳动是太极之用流行的表现,阴静则是太极之体得以定立的状态。按这里所说,不能说太极是体,阴阳是用,或太极是体,动静是用,也不能说阳动是太极之体,阴静是太极之用。因为,阴和阳同是现象层次,太极是本体层次,故不能说阳动是现象层次的用,阴静就是本体层次的体;只是说,阳动可以见太极之用的流行,阴静可以显示太极之体的定立。朱子《答杨子直书》说,他一开始曾经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后来不再用体用的关系去界定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出,在《太极解义》初稿写成的时期,朱子从《太极图说》文本出发,更为关注的是太极动静的问题,而不是太极阴阳的问题。阴阳是存在的问题,动静是运动的问题,本体与此二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朱子总论自上至下的前三图说:
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余欠也。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太极),无假借也。[2]这显然是依据《太极图说》的文字来加以解释,《太极图说》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3]《太极图说》本来就是阐发太极图的文字,朱子要为太极图作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太极图说》本身并加以解释,于是就难免和他的《太极图说解》有所重复。这里“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指明了“无极”的意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这比《太极图说》第一句的解释之所指,更为清楚。
图解接着说“乾男、坤女,以气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又说“万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4]。这和《太极图说》解也类似:“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5]不同的是,在图解这里的重点是区分“气化”和“形化”。
以下谈到圣人与主静:
惟圣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极)之体用也。是以一动一静,各臻其极,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动之中。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太极)于是乎立。[6]这里对圣人提出了新的理解,不是按照《太极图说》本文那样,只从“得其秀而最灵”的生理基础去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是从“全乎太极之体用”的德行来理解圣人的境界。即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够完全实现太极之用,完全定立太极之体。具体来说,是以中正仁义贯穿动静,而以静为主,于是“人极”便得以确立起来了。人极就是人道的根本标准,人极与太极是贯通的,人能全乎太极便是人极之立。
二、“太极”“动静”阴阳论
现在我们来看《太极图说》解。
周敦颐《太极图说》本身,最重要的是七段话,朱子的解义也主要是围绕这七段话来诠释的。
第一段,无极而太极。
朱子注: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7]这是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解释无极,用“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解释太极,并且强调,无极只是太极无声无臭的特性,并不是太极之外的独立实体。这就从根本上截断了把《太极图说》的思想理解为道家的无能生有的思想的可能性。这也就点出,《太极图说》在根本上是一太极本体论体系,或太极根源论的体系。“枢纽”同中枢,“造化之枢纽”指世界变化运动系统中其主导作用的关键。“根柢”即根源,“品汇之根柢”指万物的根源。枢纽的提法表示,太极的提出及其意义,不仅是面对世界的存在,更是面对世界的运动,这也是《太极图说》本文所引导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太极图解》第一段对太极所做的“本体”解释相比,《太极图说解》的第一段解释中却没有提及本体这一概念,也许可以说,在《太极图说解》中,“本体”已化为“枢纽”和“根柢”。前者针对动静而言,后者针对阴阳而言。
第二段,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注: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8]朱子《太极解义》的主导思想体现在这一段的解释。他首先用《通书》的思想来解说太极的动静,把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解为“天命流行”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一阴一阳往来变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也就是《通书》所说的诚之通和诚之复交替流行不已的过程,动是诚之通,静是诚之复,二者互为其根。
因此,《太极图说》的根本哲学问题,在朱子《太极解义》看来,就是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而不是像他晚年和陆九渊辩论时主张的,只把太极和阴阳的关系问题看作首要的问题。这是符合《太极图说》本文脉络的。在这个前提下,太极和阴阳的问题也被重视。因此,《太极解义》中最重要的论述是“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这两句话,先讲了太极和动静的分别及关系,又讲了太极和阴阳的分别及关系。就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言,《太极解义》的体系可称为太极本体论;就太极与阴阳的关系而言,此一体系可称为太极本源论。据朱子在写作讨论《太极解义》过程中与杨子直书,他最初是用太极为体、动静为用来理解太极与动静的关系,但后来放弃了,改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的关系。那就是说,他以前认为,太极是体,动静是太极所发的用,二者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这显然不适合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是本体和载体的关系,把动静作为载体,这就比较适合太极和动静的关系了。本然之妙表示太极既是本体,又是动静的内在原因(动力因),“妙”字就是特别用来处理与动静关系的、用来说明运动根源的,这也是中国哲学长久以来的特点。与《周易》传统以“神”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不同,朱子以“道”即太极作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
“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则明确用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区别太极与阴阳,即太极是形而上的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二者有清楚的分别。把太极明确界定为道,这样就与把太极解释为理,更为接近了。
“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著是显著的用,微是内在深微的体。从微的角度看,太极就是动静阴阳之理,在内在的体;从著的角度看,动静阴阳运行变化不同,是表现著的用。所以,朱子认为太极和动静阴阳还是存在着体用的分别。特别是,这里直接以太极为理,为动静阴阳之理,提出理和动静阴阳始终是结合一起的,强化了理的意义。朱子认为,既不能说从某一个时期开始理和动静阴阳二者才相结合,也不能说将在某一个时期二者将会分离。太极始终是内在于动静和阴阳的。本来,在宇宙论上,动静就是阴阳的动静,但由于《太极图说》讲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地说,动静就成为先在于阴阳、独立于阴阳的了。
第三段,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朱子注: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9]
如果说第二段的解释关注在动静,这一段的解释关注的中心则在阴阳。从太极的动静,导致阴阳的分化与变合;有阴阳的一变一合,则产生了五行的分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这是一套由阴阳五行展开的宇宙生化论。与前面第二段不同,这里对太极的定义不是从动静的枢纽来认识太极,而是从阴阳的所以然根据来认识太极。或者说,前面是从“所以动静者”来认识太极,这里是从“所以阴阳者”界定太极。“所以为阴阳者”的视角就是存在的视角,而不是运动的视角了。至于“太极之本然”,即是《太极图解》的“本体”,“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所以阴阳者”的观念本来自二程,区分“阴阳”和“所以阴阳”,认为前者是形而下者,后者是形而上者,这种思维是朱子从程颐吸取的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对照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和吕祖谦的《太极图义质疑》,可以明显看出朱子此时的哲学思维的优势,这也是何以张、吕对朱子解义的意见只集中在“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一句,而对其太极本体论、太极根源论、太极生化论并未提出意见的原因。
三、“太极”本性论
从第四段开始,由太极动静阴阳论转到太极本性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注:
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10]前面已经说过,宇宙中处处是阴阳,而凡有阴阳处必有所以为阴阳者,这就是“无适而非阴阳”“无适而非太极”。阴阳分化为五行,五行发育为万物,万物中也皆有太极,故说“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各具于事物之中的太极即是事物之性,太极就是“性之本体”,这就转到了万物的本性论。万物因气禀不同而造成“各一其性”,即各异其性、各有各的性,互不相同。“各一其性”是说明万物由气禀不同带来的性的差异性。但朱子同时强调,太极无不具于每一物之中,这才真正体现出“性无所不在”的原理。这样朱子的解释就有两个“性”的概念,一个是“各一其性”的性,一个是“太极之全体”的性,前者是受气禀影响的、现实的、差别的性,后者是不受气禀影响的本然的、本体的、同一的性。故每一个人或物都具备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但这种具备不是部分地具有,而是全体地具有。每一个人或物都具有一太极之全体作为自己的本性。这是朱子对《太极图说》自身思想的一种根本性的发展,即从各一其性说发展为各具太极说。
第五段,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朱子注:
夫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无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所谓“妙合”者也。“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矣。[11]
上段最后讲性无不在,这里接着把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也作为性无不在的证明。这就是说,气质所禀与二五之精相联系,太极本体与无极之真相对应,各一其性与各具太极混融无间,此即性无不在的体现。重要的是,此段明确声明:“‘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这就把无极之真,同时也把太极解释为“理”了,把太极和理贯通,由此打开了南宋理气论哲学的通途。当然,太极也仍被确定为“性”,“性为之主”本是胡宏的思想,这里显示出湖湘学派把太极理解为性对朱子仍有影响。这里的性为之主,也从特定方向呼应了太极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的意义。“以理言”和“以气言”的分析使得理气论正式登上道学思想的舞台。没有《太极解义》,朱子学的理气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哲学论述。
对照《太极图解》可知,太极本性论是朱子《太极解义》的重要思想。朱子强调,男与女虽然各有其性,互不相同,但男与女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男女一太极也”。万物各异其性,而万物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万物一太极也”。尤其是,这里提出了万物各具的太极与宇宙本体的太极的关系,朱子认为,“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是万物的存在总体,其存在的根据是太极,而每一个人或物,也具有此一太极为其本性。每个人或物对宇宙总体而言是分,但每个人或物具有的太极并不是分有了太极的部分,而是全体,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后来朱子在《语类》中反复申明了这个道理。如朱子与张栻书所讨论的,朱子认为“各具一太极”的说法意在强调“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用太极的概念来表达性理学的主张。
四、“全体太极”之道
以下开始转到人生论。
第六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朱子注:
此言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也。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然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而五性之殊,散为万事。盖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圣人全体太极有以定之,则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而违禽兽不远矣。[12]
“全”或“全体”是《太极解义》后半部的重要概念,是属于人生境界与功夫论的概念。朱子认为,人物之生,皆有太极之道,此太极之道即人与物生活、活动的总原则,也是人与物的太极之性的体现。物所禀的气浑浊不清,故不能有心,亦不可能实现太极之道。只有人独得气禀之秀,其心最灵,才有可能使人不失其太极本性,体现天地之心,确立人极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皆能如此,唯有圣人能“全体太极”,即完全体现太极,完全体现太极之道和太极之性,真正确立人极。这也就是下段所说的“定”和“立人极焉”。
第七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注: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而圣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若程子论乾坤动静,而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亦此意尔。[13]
《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开始,以人极为结束,而人极的内涵是中正仁义而主静,中正仁义是基本道德概念,主静是修养方法,以人极而兼有二者,这在儒学史上是少见的。但《荀子》中也谈到静的意义,《礼记》的《乐记》本来强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故“静”在儒学史上也曾受到注意,尤其是《乐记》的思想在宋代道学中很受重视,在这个意义上,主静的提出不能仅看作受到佛道修养的影响。但对朱子和南宋理学而言,必须对主静做出新的论证。
根据六、七两段的朱子注,他提出,众人虽然具动静之理,即具有太极,但常常失之于动,其表现是“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即欲望、情欲的妄动,对私利的追逐,必须以人极“定”之,“定”是对于“失之于动”的矫正,也是使人不至失之于动的根本方法。所以在朱子的解释中,静与定相通,一定要分别的话,可以说静是方法,定还是目的,这就是“于此乎定矣”。
在第六段朱子注强调“不失其性之全”“圣人全体太极”,在第七段,又提到“圣人全动静之德”“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全体”就是全幅体现,是一实践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全动静之德,是特就人对动静之理的体现而言,全动静之德的人,就不会失之于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行事中正仁义,因此全动静之德就是全太极之道,全体太极也就是全体太极之道,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在第七段之后,朱子还说:“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14]我们记得,在《太极图解》中也说过“全乎(太极)之体用也”,这些都是相同的意思。
当然,由于《太极图说》本文强调主静,故朱子也同意“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为什么要本于静、主于静?照朱子说,这是因为“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即是说,静是体,动是用,所以以主静为本。《太极图解》比《太极图说解》这里说得更具体:“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者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极)于是乎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朱子与张栻、吕祖谦做了反复的讨论。此外朱子也指出,主静所指的这种“静”不是专指行为的,而是指心的修养要达到“此心寂然无欲而静”。这当然是合乎周子本人主张的“无欲故静”的。
应当指出,朱子《太极解义》中在论及主静时没有提到程颐的主敬思想,只在一处提及“敬则欲寡而理明”,这对于在己丑之悟已经确认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宗旨的朱子,是一欠缺。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重视程门主敬之法,对朱子是一个重要补充。
五、《太极解义》引起的哲学论辩
朱子《太极解义》文后有《附辩》,其中提到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或谓)和三种次要的反对意见(有谓)。朱子简单叙述了这些意见: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15]
所谓“读者病其分裂已甚”,应是张栻的意见(张栻《寄吕伯恭》)。四个“或谓”中,第一个“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应是廖德明的意见(朱子《答廖子晦一》);第二个“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应是吕祖谦的意见(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第三个“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是吕祖谦的意见(张栻《答吴晦叔》),第四个“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应是张栻的意见(朱子《答张敬夫十三》)。至于“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应该都与张栻、吕祖谦的意见有关。
朱子在《附辩》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回应:
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陈来朱子于乾道己丑(1169)春中和之悟后,在将中和之悟报告张栻等湖南诸公的同时,即开始了他的哲学建构。当年六月他刊行了建安本《太极通书》,接着写作《太极图解》和《太极图说解》,二者合称《太极解义》。次年春,《太极解义》完成,他立即寄给当时在严州的张栻和吕祖谦,此后数年在与张、吕的讨论中不断修改,至乾道癸巳年(1173)定稿。
一、“太极”本体论
让我们先来看《太极图解》。由于图解的图形不易印刷,我们这里把代表太极、阴阳的图形直接转为概念,使文句明白通贯,便于讨论。
对于太极图最上面的第一圆圈,朱子注:
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1]这是说第一圆圈就是指代《太极图说》的首句“无极而太极”,而落实在“太极”,因为所谓“无极而太极”就是指“无形无象的太极”。朱子解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即把“本体”作为道学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这一“本体”概念在图解中反复出现,成为《太极图解》哲学建构的突出特点。这也是二程以来道学所不曾有过的。照朱子的解释,太极是动静阴阳的本体,此一本体乃是动静阴阳之所以然的根据和动力因。而这一作为本体的太极并不是离开阴阳的独立存在者,它即阴阳而不杂乎阴阳。“即阴阳”就是不离乎阴阳,“不杂乎阴阳”说明太极并不是阴阳,也不是与阴阳混合不分。这一“不离不杂”的说法开启了朱子学理解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存在关系模式。
对于太极图的第二圆圈,就是所谓坎离相抱图,他认为左半边是阳之动,右半边代表阴之静,而包围在中间的小圆圈则是太极。他指出,太极“其本体也”,意味太极是阳动阴静的本体;又说,阳之动,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阴之静,是“太极之体所以立也”。这就区分了太极的体和用,认为阳动是太极之用流行的表现,阴静则是太极之体得以定立的状态。按这里所说,不能说太极是体,阴阳是用,或太极是体,动静是用,也不能说阳动是太极之体,阴静是太极之用。因为,阴和阳同是现象层次,太极是本体层次,故不能说阳动是现象层次的用,阴静就是本体层次的体;只是说,阳动可以见太极之用的流行,阴静可以显示太极之体的定立。朱子《答杨子直书》说,他一开始曾经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后来不再用体用的关系去界定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出,在《太极解义》初稿写成的时期,朱子从《太极图说》文本出发,更为关注的是太极动静的问题,而不是太极阴阳的问题。阴阳是存在的问题,动静是运动的问题,本体与此二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朱子总论自上至下的前三图说:
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余欠也。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太极),无假借也。[2]这显然是依据《太极图说》的文字来加以解释,《太极图说》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3]《太极图说》本来就是阐发太极图的文字,朱子要为太极图作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太极图说》本身并加以解释,于是就难免和他的《太极图说解》有所重复。这里“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指明了“无极”的意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这比《太极图说》第一句的解释之所指,更为清楚。
图解接着说“乾男、坤女,以气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又说“万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4]。这和《太极图说》解也类似:“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5]不同的是,在图解这里的重点是区分“气化”和“形化”。
以下谈到圣人与主静:
惟圣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极)之体用也。是以一动一静,各臻其极,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动之中。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太极)于是乎立。[6]这里对圣人提出了新的理解,不是按照《太极图说》本文那样,只从“得其秀而最灵”的生理基础去谈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是从“全乎太极之体用”的德行来理解圣人的境界。即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够完全实现太极之用,完全定立太极之体。具体来说,是以中正仁义贯穿动静,而以静为主,于是“人极”便得以确立起来了。人极就是人道的根本标准,人极与太极是贯通的,人能全乎太极便是人极之立。
二、“太极”“动静”阴阳论
现在我们来看《太极图说》解。
周敦颐《太极图说》本身,最重要的是七段话,朱子的解义也主要是围绕这七段话来诠释的。
第一段,无极而太极。
朱子注: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
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7]这是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解释无极,用“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解释太极,并且强调,无极只是太极无声无臭的特性,并不是太极之外的独立实体。这就从根本上截断了把《太极图说》的思想理解为道家的无能生有的思想的可能性。这也就点出,《太极图说》在根本上是一太极本体论体系,或太极根源论的体系。“枢纽”同中枢,“造化之枢纽”指世界变化运动系统中其主导作用的关键。“根柢”即根源,“品汇之根柢”指万物的根源。枢纽的提法表示,太极的提出及其意义,不仅是面对世界的存在,更是面对世界的运动,这也是《太极图说》本文所引导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太极图解》第一段对太极所做的“本体”解释相比,《太极图说解》的第一段解释中却没有提及本体这一概念,也许可以说,在《太极图说解》中,“本体”已化为“枢纽”和“根柢”。前者针对动静而言,后者针对阴阳而言。
第二段,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注: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故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8]朱子《太极解义》的主导思想体现在这一段的解释。他首先用《通书》的思想来解说太极的动静,把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解为“天命流行”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一阴一阳往来变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也就是《通书》所说的诚之通和诚之复交替流行不已的过程,动是诚之通,静是诚之复,二者互为其根。
因此,《太极图说》的根本哲学问题,在朱子《太极解义》看来,就是太极和动静的关系。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而不是像他晚年和陆九渊辩论时主张的,只把太极和阴阳的关系问题看作首要的问题。这是符合《太极图说》本文脉络的。在这个前提下,太极和阴阳的问题也被重视。因此,《太极解义》中最重要的论述是“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这两句话,先讲了太极和动静的分别及关系,又讲了太极和阴阳的分别及关系。就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言,《太极解义》的体系可称为太极本体论;就太极与阴阳的关系而言,此一体系可称为太极本源论。据朱子在写作讨论《太极解义》过程中与杨子直书,他最初是用太极为体、动静为用来理解太极与动静的关系,但后来放弃了,改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的关系。那就是说,他以前认为,太极是体,动静是太极所发的用,二者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这显然不适合太极与动静的关系。而本然之妙和所乘之机,是本体和载体的关系,把动静作为载体,这就比较适合太极和动静的关系了。本然之妙表示太极既是本体,又是动静的内在原因(动力因),“妙”字就是特别用来处理与动静关系的、用来说明运动根源的,这也是中国哲学长久以来的特点。与《周易》传统以“神”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不同,朱子以“道”即太极作为妙运万物的动力因。
“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则明确用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区别太极与阴阳,即太极是形而上的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二者有清楚的分别。把太极明确界定为道,这样就与把太极解释为理,更为接近了。
“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虽然,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著是显著的用,微是内在深微的体。从微的角度看,太极就是动静阴阳之理,在内在的体;从著的角度看,动静阴阳运行变化不同,是表现著的用。所以,朱子认为太极和动静阴阳还是存在着体用的分别。特别是,这里直接以太极为理,为动静阴阳之理,提出理和动静阴阳始终是结合一起的,强化了理的意义。朱子认为,既不能说从某一个时期开始理和动静阴阳二者才相结合,也不能说将在某一个时期二者将会分离。太极始终是内在于动静和阴阳的。本来,在宇宙论上,动静就是阴阳的动静,但由于《太极图说》讲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地说,动静就成为先在于阴阳、独立于阴阳的了。
第三段,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朱子注: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阳也,火、金,阴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9]
如果说第二段的解释关注在动静,这一段的解释关注的中心则在阴阳。从太极的动静,导致阴阳的分化与变合;有阴阳的一变一合,则产生了五行的分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这是一套由阴阳五行展开的宇宙生化论。与前面第二段不同,这里对太极的定义不是从动静的枢纽来认识太极,而是从阴阳的所以然根据来认识太极。或者说,前面是从“所以动静者”来认识太极,这里是从“所以阴阳者”界定太极。“所以为阴阳者”的视角就是存在的视角,而不是运动的视角了。至于“太极之本然”,即是《太极图解》的“本体”,“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所以阴阳者”的观念本来自二程,区分“阴阳”和“所以阴阳”,认为前者是形而下者,后者是形而上者,这种思维是朱子从程颐吸取的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对照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和吕祖谦的《太极图义质疑》,可以明显看出朱子此时的哲学思维的优势,这也是何以张、吕对朱子解义的意见只集中在“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一句,而对其太极本体论、太极根源论、太极生化论并未提出意见的原因。
三、“太极”本性论
从第四段开始,由太极动静阴阳论转到太极本性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注:
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10]前面已经说过,宇宙中处处是阴阳,而凡有阴阳处必有所以为阴阳者,这就是“无适而非阴阳”“无适而非太极”。阴阳分化为五行,五行发育为万物,万物中也皆有太极,故说“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各具于事物之中的太极即是事物之性,太极就是“性之本体”,这就转到了万物的本性论。万物因气禀不同而造成“各一其性”,即各异其性、各有各的性,互不相同。“各一其性”是说明万物由气禀不同带来的性的差异性。但朱子同时强调,太极无不具于每一物之中,这才真正体现出“性无所不在”的原理。这样朱子的解释就有两个“性”的概念,一个是“各一其性”的性,一个是“太极之全体”的性,前者是受气禀影响的、现实的、差别的性,后者是不受气禀影响的本然的、本体的、同一的性。故每一个人或物都具备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但这种具备不是部分地具有,而是全体地具有。每一个人或物都具有一太极之全体作为自己的本性。这是朱子对《太极图说》自身思想的一种根本性的发展,即从各一其性说发展为各具太极说。
第五段,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朱子注:
夫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无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所谓“妙合”者也。“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矣。[11]
上段最后讲性无不在,这里接着把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也作为性无不在的证明。这就是说,气质所禀与二五之精相联系,太极本体与无极之真相对应,各一其性与各具太极混融无间,此即性无不在的体现。重要的是,此段明确声明:“‘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这就把无极之真,同时也把太极解释为“理”了,把太极和理贯通,由此打开了南宋理气论哲学的通途。当然,太极也仍被确定为“性”,“性为之主”本是胡宏的思想,这里显示出湖湘学派把太极理解为性对朱子仍有影响。这里的性为之主,也从特定方向呼应了太极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的意义。“以理言”和“以气言”的分析使得理气论正式登上道学思想的舞台。没有《太极解义》,朱子学的理气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哲学论述。
对照《太极图解》可知,太极本性论是朱子《太极解义》的重要思想。朱子强调,男与女虽然各有其性,互不相同,但男与女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男女一太极也”。万物各异其性,而万物所具的太极是相同的,这就是“万物一太极也”。尤其是,这里提出了万物各具的太极与宇宙本体的太极的关系,朱子认为,“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是万物的存在总体,其存在的根据是太极,而每一个人或物,也具有此一太极为其本性。每个人或物对宇宙总体而言是分,但每个人或物具有的太极并不是分有了太极的部分,而是全体,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后来朱子在《语类》中反复申明了这个道理。如朱子与张栻书所讨论的,朱子认为“各具一太极”的说法意在强调“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用太极的概念来表达性理学的主张。
四、“全体太极”之道
以下开始转到人生论。
第六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朱子注:
此言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也。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然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而五性之殊,散为万事。盖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圣人全体太极有以定之,则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人极不立,而违禽兽不远矣。[12]
“全”或“全体”是《太极解义》后半部的重要概念,是属于人生境界与功夫论的概念。朱子认为,人物之生,皆有太极之道,此太极之道即人与物生活、活动的总原则,也是人与物的太极之性的体现。物所禀的气浑浊不清,故不能有心,亦不可能实现太极之道。只有人独得气禀之秀,其心最灵,才有可能使人不失其太极本性,体现天地之心,确立人极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皆能如此,唯有圣人能“全体太极”,即完全体现太极,完全体现太极之道和太极之性,真正确立人极。这也就是下段所说的“定”和“立人极焉”。
第七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注: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而圣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若程子论乾坤动静,而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亦此意尔。[13]
《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开始,以人极为结束,而人极的内涵是中正仁义而主静,中正仁义是基本道德概念,主静是修养方法,以人极而兼有二者,这在儒学史上是少见的。但《荀子》中也谈到静的意义,《礼记》的《乐记》本来强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故“静”在儒学史上也曾受到注意,尤其是《乐记》的思想在宋代道学中很受重视,在这个意义上,主静的提出不能仅看作受到佛道修养的影响。但对朱子和南宋理学而言,必须对主静做出新的论证。
根据六、七两段的朱子注,他提出,众人虽然具动静之理,即具有太极,但常常失之于动,其表现是“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即欲望、情欲的妄动,对私利的追逐,必须以人极“定”之,“定”是对于“失之于动”的矫正,也是使人不至失之于动的根本方法。所以在朱子的解释中,静与定相通,一定要分别的话,可以说静是方法,定还是目的,这就是“于此乎定矣”。
在第六段朱子注强调“不失其性之全”“圣人全体太极”,在第七段,又提到“圣人全动静之德”“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全体”就是全幅体现,是一实践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全动静之德,是特就人对动静之理的体现而言,全动静之德的人,就不会失之于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行事中正仁义,因此全动静之德就是全太极之道,全体太极也就是全体太极之道,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在第七段之后,朱子还说:“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14]我们记得,在《太极图解》中也说过“全乎(太极)之体用也”,这些都是相同的意思。
当然,由于《太极图说》本文强调主静,故朱子也同意“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为什么要本于静、主于静?照朱子说,这是因为“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即是说,静是体,动是用,所以以主静为本。《太极图解》比《太极图说解》这里说得更具体:“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阳动)者也,太极之用之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中正仁义,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则人(极)于是乎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朱子与张栻、吕祖谦做了反复的讨论。此外朱子也指出,主静所指的这种“静”不是专指行为的,而是指心的修养要达到“此心寂然无欲而静”。这当然是合乎周子本人主张的“无欲故静”的。
应当指出,朱子《太极解义》中在论及主静时没有提到程颐的主敬思想,只在一处提及“敬则欲寡而理明”,这对于在己丑之悟已经确认了“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宗旨的朱子,是一欠缺。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重视程门主敬之法,对朱子是一个重要补充。
五、《太极解义》引起的哲学论辩
朱子《太极解义》文后有《附辩》,其中提到四种主要的反对意见(或谓)和三种次要的反对意见(有谓)。朱子简单叙述了这些意见: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15]
所谓“读者病其分裂已甚”,应是张栻的意见(张栻《寄吕伯恭》)。四个“或谓”中,第一个“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应是廖德明的意见(朱子《答廖子晦一》);第二个“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应是吕祖谦的意见(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第三个“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是吕祖谦的意见(张栻《答吴晦叔》),第四个“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应是张栻的意见(朱子《答张敬夫十三》)。至于“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应该都与张栻、吕祖谦的意见有关。
朱子在《附辩》中对这些意见做了回应:
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16]
这是关于阴阳观的讨论,在朱子看来,阴阳变化流行,属于阳动;而成型固定,属于阴静。认为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继之者善和成之者性的分别。所以把继之者善作为阳动,把成之者性作为阴静,这是很自然的。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17]
太极是理,无形无象,阴阳是气,已属形象,二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这是二程哲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朱子完全继承了这一点。特别把道器的分别运用于理气的分析。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18]朱子认为,仁义中正如同元亨利贞,既然在《通书》中元亨属于诚之通,利贞属于诚之复,则四德之中,元亨与利贞之间就有体用之分。同理,中正仁义也就可以有体用之分。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19]
这是朱子用吕祖谦的意思回应张栻的怀疑。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云:“‘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20]朱子吸取了吕氏的这一意见。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21]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张拭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就不是一源了。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理是体,事物是用,一源是言体言理,无间是言用言事;言理体先而用后,言事先用而后体,二者角度不同。所以朱子认为,虽然,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但二者在形而上学上可分为先后。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22]
最后这点较为复杂。照“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的质疑,这是反对把仁归属于阳动,认为仁是包含四德的统体,怎么能把仁只归结为一个特定方面呢?朱子的辩解是,《太极图说》以“仁”配“义”,然后以“仁义”与“中正”相对,这说明《太极图说》中的仁不是专言包四德的仁,从而也就不是“统体”的仁,只是偏言的仁、分别而言的仁。这个仁是义之体,义是仁之质,具有体用的差别。朱子此段回应的对象不甚确定,参与太极解义之辩的人中,只有吕祖谦《答朱侍讲六》提及仁包四德,但所论与这里所说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这几条都和体用问题有关,而张栻颇注重体用之论,吕祖谦也就体用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可见体用问题是太极解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总之,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美〕田浩
在学术思想繁荣发展的12世纪,朱熹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互动使得他最终可以升至经典的权威解读者以及道学群体的领军人物。在宋代,相比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6~2017)先生所使用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指比“理学”更广的范畴,道学的含义要具体得多。但道学要远比陈荣捷(1901~1994)教授所提出的“新儒学”——专指被二程及朱熹所发扬的思想流派——宽泛得多。[1]一些学者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词汇的差异或仅仅关注于道学在1181年后的发展,所以他们或者将“道学”与陈荣捷先生的“新儒学”混为一谈;或者继续将“新儒学”与“理学”这二者假设成等同为一。[2]中国学者经常使用“学派”这一标签来称呼湖湘、浙东之类的地域分支,然而“道学”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范畴。相较于宋代所形成的思想学派而言,这种打着“学派”标签的地域分支常给西方学者一种有更强的凝聚力、高度一致性及范围更广泛的感觉,所以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否定这类地方团体等同于一个学派。
在和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当中,起先是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其后是陈亮(1143~1194)和陆九渊(1139~1193)等人,他们不但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贡献了若干思想概念,而且朱熹在回应他们的观点或立场的过程中,他们也启发或刺激了朱熹更进一步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为了突出朱熹同时代学者的重要性,田浩曾以个案研究对比朱熹早期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及其后来与陈亮、陆九渊的互动,以及朱熹如何在1181年为吕祖谦写的悼词中开始宣称他自己是道学唯一的权威。他在悼词中大声疾呼:“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新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3]1181年之后,朱熹在道学群体中变得更为重要,他有时甚至对其他学者不屑一顾。
朱熹对其同时代儒家的品评影响了宋代以后直至20世纪的学者,因此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重视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甚或将他们描述为与朱熹思想完全敌对的竞争者。在阅读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时,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一个转折点,许多中国学者对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他们进行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蔡方鹿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4],朱汉民、陈谷嘉的《湖湘学派源流》[5],潘富恩、徐余庆的《吕祖谦评传》[6],张立文对陆九渊的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7],徐纪芳则探讨了陆九渊的弟子情况[8]。田浩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对陈亮的思想及其与朱熹的论辩给予了正面积极的重新评价,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观点开始在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此外,他在1992年出版了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His'sAscendancy,即《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其1996年出版了中文版,并于2009年增订《朱熹的思维世界》,论述了与朱熹同时代儒家对朱熹思想观念及道学权威的影响要远比传统观点所承认的要大得多。田浩的著作及其与狄百瑞在《东西方哲学》[9]上的辩论,唤起学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将这些学者一方面视为自身强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视为在道学发展及朱熹思想主流化过程中的关键对话者。因此田浩的论著大致可以代表这一个重大转折,即将朱熹置身于与其同时代学者环境中来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强调朱熹同时代思想家的贡献和他们致力于社会政治的改革与提升道德修养的努力延续了这一转折。比如余英时对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蓝图给予了极大关注。[10]
因此本文以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也简短亮相,帮助传达这些主要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展示朱熹时代儒家团体的分支之内与之间各种思想的消长。虽然许多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没有在20世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相当可观,所以本文只能选取其中一些成果来加以说明。本文介绍学界所涌现的大量相关研究目的在于以此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变。总之,因为共同尊奉儒家经典及北宋主要的儒学家,使得朱熹与同时代的儒学家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
一、张栻与湖湘学派
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即今天的湖南、湖北一带,在公元12世纪变得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外来家族:从福建北部迁来的胡氏家族和四川迁来的张氏家族。胡安国(1074~1138)宣称自己是二程的追随者,奠定了道学湖湘学派的思想基石。此外胡安国还与二程的早期门人杨时(1053~1135)一起编纂了一本记录二程语录的早期版本。胡安国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春秋》的注解,其中强调抵抗“蛮夷”,这一注本后来成为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官方经典注本。胡安国去世之后,宋朝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以保证胡家的经济来源。胡宏的著作《皇王大纪》继续关注国家的历史与政治,这种关注在他的早期作品《知言》中也相当明显。虽然很多学者关注胡宏在《知言》有关“性”的阐发,叶翰教授论证了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不断变化的正统和对外族的征讨等政治议题构成了这部书的主要框架。其书第一章讨论天心与天命,最后一章讨论宋朝被女真占领的“中原”地区。与通常对“体”和“理”的哲学解释不同,胡宏认为这些概念意味着统贯、治理、条理事物的意思。[11]因此他醉心于重建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古代理想模式——井田制,即国家分给家族或宗族土地作为经济或制度的基础。
大多数学者关注《知言》怎么从思想层面来解释“心”和“性”的含义,但这一点遭到朱熹的质疑与谴责。胡宏论及“天命为性,人性为心”12]。又如:“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13]朱熹认为胡宏误解了“性”的含义,而将心和人的情感相混淆。朱熹认为人性的本质就像天理存于人性一样,因此他批评胡宏忽略了人性和天理的重要性。而且,朱熹认为“天理”或“理”内在于人性之中,而胡宏将“理”作为人行为的目标。虽然胡宏对佛学怀有敌意,但朱熹认为胡宏有关“心”和“性”概念源于佛教。[14]尽管如此,胡宏认为自己是道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告诫他的学生:“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5]张栻是胡宏学生并继承他的道学使命,继续修订《知言》,同时他还是主战派领袖宰相张浚(1097~1164)之子。因为有如此非凡的背景,加之他的学识和仕途经历以及他在长沙主讲岳麓书院多年,所以张栻从1164年至1168年成为道学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并不奇怪。他和吕祖谦被认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还曾称赞张栻为“道学之懿,为世醇儒”[16]。
17世纪的中国首部思想史《宋元学案》给张栻以不朽的评价:“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17]基于这个评价,牟宗三(1909~1995)进一步评价认为,相比朱熹和陆九渊,张栻则更接近孟子。牟先生同时指出张栻没有成功地维护程颢和胡宏的孟子传统,也正因为张栻后来认同了朱熹的观点最终导致朱熹的非正统观点成为宋代至20世纪的正统思想。虽然田浩对牟先生有关张栻与程颢两人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湖湘学派衰微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田浩强调张栻生前对朱熹观点的影响,主要是“修身”和“仁”方面。从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对张栻的研究来看,以上观点也得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回应。[18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足以论证这一点:向世陵称赞张拭是湖湘学派的整合者,不过他也认为张栻从来没有对胡宏“性”的观点有所创新,同时在与朱熹争论的过程中张栻还放弃了湖湘学派的特色。[19]李可心则批评张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对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其哲学思想的声音为朱熹的所湮没。此外,张栻关于性与心的观点亦充满矛盾。[20]
张栻有关“心”和“性”的观点,特别是其与孟子、程颢和胡宏的关系实际非常复杂。孟子认为人心本善,程颢则以为人们不能否定恶也是人性。胡宏拓展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性”超越了善与恶,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他认为“性”是绝对的,并且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张栻通过将“人性”等同于万事万物的“理”,进一步发展了胡宏的说法。孟子将(人)性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但是他们从孟子对人性的观点中发展出自己的新观点。同时张栻并不十分认同胡宏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这也表明张栻更倾向于孟子的观点。尽管如此,孟子认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人性中比“四德”(即“仁”“义”“礼”“智”)更为基本。张栻认为“德”是人性之未发,但其已发属于心。张栻将“德”的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但其已发状态则与心联系,因此,与孟子不同,他在人性与心之间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张栻断定人性包含着所有的“理”或准则,他也表示理和心两者并无差异,没有必要将两者相整合,朱熹则否认两者是一致的。张栻曾谈及:“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21]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他认为理和心几无二致,但张栻反对将心简单地看作理。此外,他除了将“恶”解释为人的身体与其他事物互动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张栻还通过描述利与义之间的矛盾斗争进而将人欲与天理相对立。这种人性和天理之间对立性的矛盾冲突使其与“二程”中程颐的理论更加相近。[22]
近年以来,相关研究日益细致深入,尤其是有关张栻对“性”和“太极”的研究。2015年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张栻研究研讨会中所收录的论文正反映了张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3]比如其中一些论文涉及从张栻对经典的解释——尤其在《易经》和《诗经》方面——到他的礼制思想及他的教育观点与当今教育的关联等诸方面。2017年11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纪念“朱张会讲”八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分发《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4]。总而言之,近些年有关张栻的研究十分活跃,他对道学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了更加广泛的认可。
数百年以来,有关张栻思想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他对朱熹思想的影响,而非其本身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关于他在修身方面的观点。儒家经典《中庸》强调的是在情感被激发之前,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恰当的程度进而达到的一种均衡、和谐的状态。[25]程颐提高了修身的要求,他要求弟子保存和守护这种感觉,就像他们在心中被唤起一样,并在心被表达之后,检验这种感觉。身处湖湘的张栻师法胡宏,认为“性”和“心”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他主张在行动中拓展认识,而不是关注于静坐和修身中提高涵养。[26]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受到杨时的影响,杨时在福建以二程学说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学说,主张在感觉被唤起前静坐冥想,不过朱熹对杨时的方法有所不满。因为仰慕张栻的学问,朱熹在1167年前往岳麓书院与其论学。两人当面论学,张栻说服朱熹将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将已发状态与“心”相关联。朱熹回到福建之后,给张栻的四封信表明他接受了张栻的这一观点,但不久之后,朱熹就声明这四封信中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抱怨放弃了杨时静修沉思的方法后,自己在道德要求上有所下降。1169年他写信给张栻,宣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心的“体用”(实质和功能)。1172年他在《中和旧说》中的序言中,阐明了他思想的变化,以及怎样达到他所认为的正确中和观点的历程。[27]这一变化的取得一方面由于朱熹对闽学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在于他不但得益于湖湘学者的启发,而且还超越了湖湘学派,这标志着朱熹自信在思想的成熟和自己于道学中的权威方面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朱熹称张栻接受了这一新的思想体系,但是很难找到张栻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文献记载,因为朱熹在编纂张栻的文集时,并没有将张栻所有的书信和著作纳入其中。[28]
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同样也难以判断,他们有关重新解释“仁”一系列的讨论,试图纠正“仁”说陷于一偏的观点,特别是“二程”及其门人忽略“仁之爱”,过分地强调“仁之理”。几个世纪以来,朱熹对“仁”的终极定义——“爱之理”和“心之德”——一直为人所称道。相当一部分传统的和20世纪的学者断言张栻折服于朱熹的观点,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张栻最后完成的文章实际出自朱熹之手。[29尽管如此,刘述先(1934~2016)先生和田浩指出朱熹在其后与吕祖谦弟弟吕祖俭的书信中声明“心之德”的提法是张栻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起初遭到了朱熹的拒绝。[30]更重要的发现则源于陈来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张栻的《张子太极解义》,这本书说明了张拭在提升周敦颐(1017~1073)在道学中地位的重要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周敦颐地位的抬升一般被想当然地归于朱熹的功劳。[31]这些新的发现表明,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而言,近些年学界在张栻对朱熹的影响这一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二、吕祖谦与浙东学派
浙东(今属浙江)儒者与湖湘地区的儒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二程道学的两大分支——胡氏家族与吕氏家族之间的友谊。张九成(1092~1159)是联结这两个地区的另外一个纽带,他的心学观念对胡氏及吕氏家族皆有影响。[32]此外浙东与湖湘儒者都有着对国家强烈的使命感,而且他们都极力主张赶走占领中原腹地的女真人。因为吕氏家族从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末涌现了许多达官显贵和知名学者,这种家族的光环对吕祖谦的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带着吕氏家族对宋王朝的忠诚和乐观,他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编纂史学、制度方面的著作,以求更好地理解和改进治国之道。
吕氏家族长期以来以其博学,即精通中原文献而闻名,同时并不局限于师承一家的狭隘学派思想。就像蒋伟胜认为,吕家中原文献的藏书注重北宋特别是“二程”及张载(1020~1077)的著作,这也成为吕祖谦思想的核心观点。[33]因此吕祖谦非常自然地表达他治学方法(被牟宗三总结为“一元”论,被马恺之称为“有机”)[34]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将经典和历史、修身、政治及制度活动相结合。[35]他对道学早期思想家的贡献持认可态度,并试图保存他们著作的原貌,所以他曾批评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评点。[36]在此之前,他还为了维护胡宏的原本而反对朱熹修订、改变胡宏的《知言》。基于程颢、张九成、张栻对“心”的强调,吕祖谦直接通过“理”来分析“心”。与此相反朱熹关注程颐的“性即理”来建立他有关人性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心即是理。朱熹倾向把天理和人欲视作互相敌对的二元,吕祖谦认为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人的情感会寻求和谐甚至互相融合。因此吕祖谦在修身方法上更加倾向于张栻,即在行动中审视自己的实践,而不是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先冥想而后再实践。
吕祖谦认为修身应更多地在现实世界多加实践并学习“实学”,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浙东儒学一大特征。这种实学也运用了这样的口号“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和“切用于世”[37]。因为吕祖谦思想当中修身和实学互相融合,正如事功学、功利学说与朱熹的道学学说有某些互通之处一样,所以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38]
吕祖谦和朱熹主要的合作在于书院教育方面。田浩曾强调他们两人对书院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论及吕祖谦对朱熹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在朱熹从事书院教学之前,吕祖谦就有大量的门生,还有怎样发展书院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吕祖谦帮助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还为这座著名的宋代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朱熹为他的学生制定治学方向,并通过书院教学来提升其在经典解读及道学正统方面的权威地位,后来朱熹在这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在书院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快使其故去的友人黯然失色。
因为致力于治国之道的研究,吕祖谦将其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研究古代和当时历史的演变,以求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从中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比如他曾告诫学生应该从历史中观察事物如何变化,而不是将历史只看作记忆中的大量历史事件。吕祖谦还对其门生提到,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该先停下来设身处地地考虑,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39]吕祖谦的许多史学著作是在讲学的同时完成的,比如他所作的《东莱博议》是为了指导学生如何在科举考试中写策论,可惜的是他的《大事记》只编到了公元前90年,在他病重直到去世前他都努力接续《左传》这一记录历史的传统。他的史学著作特别关注制度的发展,比如他的《历代制度详说》辑录了历代制度方面的史料。
吕祖谦和朱熹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些主要区别。朱熹特别注重经的地位,吕祖谦则认为经与史同等重要。同时他们两人都认为上古三代才是黄金时代,朱熹将天理和修身之道作为思想的准则,但吕祖谦更关注制度所产生的历史效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关注道德问题,吕祖谦则更注重制度因素。在评论历史学家方面,朱熹首先看他们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则较少关注史学家的个性,而是注重用历史来解释历史。朱熹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历史,而吕祖谦将天理融入到历史当中。[40]
在西方学界,马恺之(Kai Marchal)教授对吕祖谦的政治思想及其与朱熹的关系有最深入的研究。这两位道学家都认为通过个人修身进德提升儒家道德理想,进而可以从根本上促成社会和国家的变革。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的道德楷模中,特别是从孟子及北宋儒家那里继承了自信。虽然两人都取法于儒家经典,相对于朱熹而言,吕祖谦更加主张儒家激进的政治改革。因此相较于吕祖谦而言,朱熹倾向于远离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而更倾向于提高个人及群体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在其最后两年对政治上的挫败感到失望,所以如果他能像朱熹一样长寿的话,他对儒家道德能在根本上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观点也许也会有所动摇。尽管如此,有关儒家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主张成为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点。[41]这些分歧无疑反映了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然而这些也是他们两人思想差异的反映。
比如吕祖谦对王安石(1021~1086)的评价就比朱熹要积极得多,如他认为王安石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虽然吕祖谦也批评了王安石,但吕祖谦表达了一个和王安石相同的目标,马恺之总结为:“通过大规模的重组国家机构以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有为的政府以应对社会和政治上的挑战。”[42]吕祖谦对制度和史学的研究不但为改革提供了具体的理念和制度,还使他比道学阵营中大多数试图通过《周礼》中理想化的描述来恢复周朝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更加务实。比如在公元780年杨炎“两税法”的推行消除了在市场上购买土地的障碍后,恢复“井田制”的目标变得日益渺茫。但吕祖谦仍然很有信心,相信通过实际努力重建宗族谱系、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在社会上恢复由来已久的秩序和儒学家庭伦理。比如他曾写到虽然全面复兴古代制度风俗十分困难,但也有可能通过限制私有财产和保留地方武装开始逐步恢复。
马恺之也反驳一些现代学者对吕祖谦的批评,同时这也是对朱熹批评吕祖谦博杂和对最基本的道德概念关注不够的回应。比如朱熹同意一位门人对吕祖谦的描述:“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43]田浩曾指出朱熹对吕祖谦怀有敌意的批评几乎都始于这位好朋友去世之后。在和陈亮以及其他浙东儒者论辩的时候,朱熹认为这是吕祖谦错误的延续。[44]中国现在也有学者指出朱熹后来尖锐批评吕祖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追求道学权威并努力限制浙东学派的影响力。[45]
与包弼德教授将吕祖谦描述为“搞分门别类的书生”[46]不同,马恺之举例说明吕祖谦将自我修身与历史中的真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吕祖谦的许多研究关注探讨自我修身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了尽到士大夫的责任进而影响国家统治,他试图说服皇帝恢复传统的官僚集团以此作为对皇帝行为的制衡。但朱熹试图说服皇帝自愿限制自己的权力,吕祖谦则认识到通过制度限制皇权的必要性。皇权倾向于朱熹而非吕祖谦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朱熹主张关注皇帝内心道德的转变相比,吕祖谦通过制度来限制皇帝行为的方法看起来不合礼法并具有敌意。因此“与其他儒者思想家相比,吕祖谦较早地意识到‘道德的内化’的政治结果”[47]。
魏希德教授也曾对吕祖谦在1168年至1181年期间的道学领导地位提出质疑,她指出为什么吕祖谦没有像朱熹一样经常使用“道学”这一概念?[48]虽然他们在许多方面互相认同或合作,但我们应该了解他们两人的差别。除了其博学和善于综合各种治学方法外,吕祖谦比朱熹更早认识到道学群体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吕祖谦反映作为道学早期的社会政治联盟,其政治理想使得他们能够容忍相当多元的儒家思想。与此相反,朱熹特别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教化或思想的目的,所以他在使用“道学”来论述他的议题时要比吕祖谦更为严格。在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的密切关注反映了他对“醇儒”的认识,并努力清除道学内部被其他思想所影响的人。作为经典和传统的诠释者,朱熹重点关注思想的纯粹性及自己的权威地位,因此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探索思想意识纯粹性的过程中,朱熹较经常使用“道学”或“道统”等术语。朱熹的这种探索不但在其1181年对吕祖谦的悼词中宣称自己在道学中的领导地位中有所表现,而且在此后十年中他面对陈亮和陆九渊的挑战时显露无遗。
总之,虽然20世纪学者大多忽略了吕祖谦,但自从1992年开始学界在此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力地支持了田浩对吕祖谦在1168年到1181年之间是最重要思想家的评价。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吕祖谦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以及“主盟斯文”,他也是社会的精英、史学家和士大夫[49];二是他建立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基础,特别将心的修养与研究历史和经典相结合[50;三是他的博学并没有削弱他和张载及二程的思想渊源,此外他投身于修身[51];四是他作为道学家领袖并不受师承或某个派别的限制[52;五是吕祖谦对朱熹的重要影响在于其对经典的认识、书院教学和编纂《近思录》等,在宋代以后他对浙东地区的儒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53]
三、结语
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并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世纪和当代学者肯定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观念和贡献的一大因素在于地域的认同,不过将这种转变仅仅归为地域的认同未免过于片面。虽然除了直接驳斥其论点,中国学者鲜少提到外国学者的著述,但他们隐含地分享田浩的观点,也对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投以更多的关注。
本文是我参与撰写的由香港中文大学黄勇、吴启超两位教授主编的《朱熹哲学的指南》(The 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一书第十二章《朱熹与其同时代的儒家》(Zhu Xi's Contemporaries)的一部分。我之所以献上此文是因为一些参加岳麓书院会议的同人们也许会对这样一个面向西方公众的概述的例子感兴趣。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从与2016~2017年度来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的两位学者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玉敏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任仁仁及普渡大学历史系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的讨论中受益良多。任仁仁还为本次会议特将中文稿译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殷慧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帮忙修改译稿。在此谨向他们略表谢忱。
16]
这是关于阴阳观的讨论,在朱子看来,阴阳变化流行,属于阳动;而成型固定,属于阴静。认为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继之者善和成之者性的分别。所以把继之者善作为阳动,把成之者性作为阴静,这是很自然的。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17]
太极是理,无形无象,阴阳是气,已属形象,二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这是二程哲学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朱子完全继承了这一点。特别把道器的分别运用于理气的分析。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18]朱子认为,仁义中正如同元亨利贞,既然在《通书》中元亨属于诚之通,利贞属于诚之复,则四德之中,元亨与利贞之间就有体用之分。同理,中正仁义也就可以有体用之分。
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19]
这是朱子用吕祖谦的意思回应张栻的怀疑。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云:“‘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20]朱子吸取了吕氏的这一意见。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21]
张栻最重视体用一源的思想,张拭以“体用一源”反对“体立而后用行”的主张,认为如果体用有先后,就不是一源了。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理是体,事物是用,一源是言体言理,无间是言用言事;言理体先而用后,言事先用而后体,二者角度不同。所以朱子认为,虽然,从实存上说理即在事物之中,但二者在形而上学上可分为先后。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22]
最后这点较为复杂。照“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的质疑,这是反对把仁归属于阳动,认为仁是包含四德的统体,怎么能把仁只归结为一个特定方面呢?朱子的辩解是,《太极图说》以“仁”配“义”,然后以“仁义”与“中正”相对,这说明《太极图说》中的仁不是专言包四德的仁,从而也就不是“统体”的仁,只是偏言的仁、分别而言的仁。这个仁是义之体,义是仁之质,具有体用的差别。朱子此段回应的对象不甚确定,参与太极解义之辩的人中,只有吕祖谦《答朱侍讲六》提及仁包四德,但所论与这里所说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这几条都和体用问题有关,而张栻颇注重体用之论,吕祖谦也就体用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可见体用问题是太极解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总之,朱子的《太极解义》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这是朱子对道学的贡献,也是他对儒学的贡献。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美〕田浩
在学术思想繁荣发展的12世纪,朱熹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互动使得他最终可以升至经典的权威解读者以及道学群体的领军人物。在宋代,相比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6~2017)先生所使用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指比“理学”更广的范畴,道学的含义要具体得多。但道学要远比陈荣捷(1901~1994)教授所提出的“新儒学”——专指被二程及朱熹所发扬的思想流派——宽泛得多。[1]一些学者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些词汇的差异或仅仅关注于道学在1181年后的发展,所以他们或者将“道学”与陈荣捷先生的“新儒学”混为一谈;或者继续将“新儒学”与“理学”这二者假设成等同为一。[2]中国学者经常使用“学派”这一标签来称呼湖湘、浙东之类的地域分支,然而“道学”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范畴。相较于宋代所形成的思想学派而言,这种打着“学派”标签的地域分支常给西方学者一种有更强的凝聚力、高度一致性及范围更广泛的感觉,所以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否定这类地方团体等同于一个学派。
在和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当中,起先是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其后是陈亮(1143~1194)和陆九渊(1139~1193)等人,他们不但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贡献了若干思想概念,而且朱熹在回应他们的观点或立场的过程中,他们也启发或刺激了朱熹更进一步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为了突出朱熹同时代学者的重要性,田浩曾以个案研究对比朱熹早期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及其后来与陈亮、陆九渊的互动,以及朱熹如何在1181年为吕祖谦写的悼词中开始宣称他自己是道学唯一的权威。他在悼词中大声疾呼:“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新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3]1181年之后,朱熹在道学群体中变得更为重要,他有时甚至对其他学者不屑一顾。
朱熹对其同时代儒家的品评影响了宋代以后直至20世纪的学者,因此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重视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甚或将他们描述为与朱熹思想完全敌对的竞争者。在阅读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时,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一个转折点,许多中国学者对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他们进行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蔡方鹿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4],朱汉民、陈谷嘉的《湖湘学派源流》[5],潘富恩、徐余庆的《吕祖谦评传》[6],张立文对陆九渊的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7],徐纪芳则探讨了陆九渊的弟子情况[8]。田浩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对陈亮的思想及其与朱熹的论辩给予了正面积极的重新评价,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观点开始在学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此外,他在1992年出版了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His'sAscendancy,即《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其1996年出版了中文版,并于2009年增订《朱熹的思维世界》,论述了与朱熹同时代儒家对朱熹思想观念及道学权威的影响要远比传统观点所承认的要大得多。田浩的著作及其与狄百瑞在《东西方哲学》[9]上的辩论,唤起学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将这些学者一方面视为自身强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视为在道学发展及朱熹思想主流化过程中的关键对话者。因此田浩的论著大致可以代表这一个重大转折,即将朱熹置身于与其同时代学者环境中来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强调朱熹同时代思想家的贡献和他们致力于社会政治的改革与提升道德修养的努力延续了这一转折。比如余英时对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蓝图给予了极大关注。[10]
因此本文以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也简短亮相,帮助传达这些主要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展示朱熹时代儒家团体的分支之内与之间各种思想的消长。虽然许多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没有在20世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相当可观,所以本文只能选取其中一些成果来加以说明。本文介绍学界所涌现的大量相关研究目的在于以此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变。总之,因为共同尊奉儒家经典及北宋主要的儒学家,使得朱熹与同时代的儒学家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
一、张栻与湖湘学派
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即今天的湖南、湖北一带,在公元12世纪变得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外来家族:从福建北部迁来的胡氏家族和四川迁来的张氏家族。胡安国(1074~1138)宣称自己是二程的追随者,奠定了道学湖湘学派的思想基石。此外胡安国还与二程的早期门人杨时(1053~1135)一起编纂了一本记录二程语录的早期版本。胡安国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春秋》的注解,其中强调抵抗“蛮夷”,这一注本后来成为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官方经典注本。胡安国去世之后,宋朝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以保证胡家的经济来源。胡宏的著作《皇王大纪》继续关注国家的历史与政治,这种关注在他的早期作品《知言》中也相当明显。虽然很多学者关注胡宏在《知言》有关“性”的阐发,叶翰教授论证了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不断变化的正统和对外族的征讨等政治议题构成了这部书的主要框架。其书第一章讨论天心与天命,最后一章讨论宋朝被女真占领的“中原”地区。与通常对“体”和“理”的哲学解释不同,胡宏认为这些概念意味着统贯、治理、条理事物的意思。[11]因此他醉心于重建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古代理想模式——井田制,即国家分给家族或宗族土地作为经济或制度的基础。
大多数学者关注《知言》怎么从思想层面来解释“心”和“性”的含义,但这一点遭到朱熹的质疑与谴责。胡宏论及“天命为性,人性为心”12]。又如:“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13]朱熹认为胡宏误解了“性”的含义,而将心和人的情感相混淆。朱熹认为人性的本质就像天理存于人性一样,因此他批评胡宏忽略了人性和天理的重要性。而且,朱熹认为“天理”或“理”内在于人性之中,而胡宏将“理”作为人行为的目标。虽然胡宏对佛学怀有敌意,但朱熹认为胡宏有关“心”和“性”概念源于佛教。[14]尽管如此,胡宏认为自己是道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告诫他的学生:“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5]张栻是胡宏学生并继承他的道学使命,继续修订《知言》,同时他还是主战派领袖宰相张浚(1097~1164)之子。因为有如此非凡的背景,加之他的学识和仕途经历以及他在长沙主讲岳麓书院多年,所以张栻从1164年至1168年成为道学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并不奇怪。他和吕祖谦被认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还曾称赞张栻为“道学之懿,为世醇儒”[16]。
17世纪的中国首部思想史《宋元学案》给张栻以不朽的评价:“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17]基于这个评价,牟宗三(1909~1995)进一步评价认为,相比朱熹和陆九渊,张栻则更接近孟子。牟先生同时指出张栻没有成功地维护程颢和胡宏的孟子传统,也正因为张栻后来认同了朱熹的观点最终导致朱熹的非正统观点成为宋代至20世纪的正统思想。虽然田浩对牟先生有关张栻与程颢两人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湖湘学派衰微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田浩强调张栻生前对朱熹观点的影响,主要是“修身”和“仁”方面。从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对张栻的研究来看,以上观点也得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回应。[18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足以论证这一点:向世陵称赞张拭是湖湘学派的整合者,不过他也认为张栻从来没有对胡宏“性”的观点有所创新,同时在与朱熹争论的过程中张栻还放弃了湖湘学派的特色。[19]李可心则批评张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对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其哲学思想的声音为朱熹的所湮没。此外,张栻关于性与心的观点亦充满矛盾。[20]
张栻有关“心”和“性”的观点,特别是其与孟子、程颢和胡宏的关系实际非常复杂。孟子认为人心本善,程颢则以为人们不能否定恶也是人性。胡宏拓展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性”超越了善与恶,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他认为“性”是绝对的,并且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张栻通过将“人性”等同于万事万物的“理”,进一步发展了胡宏的说法。孟子将(人)性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但是他们从孟子对人性的观点中发展出自己的新观点。同时张栻并不十分认同胡宏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这也表明张栻更倾向于孟子的观点。尽管如此,孟子认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人性中比“四德”(即“仁”“义”“礼”“智”)更为基本。张栻认为“德”是人性之未发,但其已发属于心。张栻将“德”的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但其已发状态则与心联系,因此,与孟子不同,他在人性与心之间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张栻断定人性包含着所有的“理”或准则,他也表示理和心两者并无差异,没有必要将两者相整合,朱熹则否认两者是一致的。张栻曾谈及:“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21]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他认为理和心几无二致,但张栻反对将心简单地看作理。此外,他除了将“恶”解释为人的身体与其他事物互动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张栻还通过描述利与义之间的矛盾斗争进而将人欲与天理相对立。这种人性和天理之间对立性的矛盾冲突使其与“二程”中程颐的理论更加相近。[22]
近年以来,相关研究日益细致深入,尤其是有关张栻对“性”和“太极”的研究。2015年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张栻研究研讨会中所收录的论文正反映了张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3]比如其中一些论文涉及从张栻对经典的解释——尤其在《易经》和《诗经》方面——到他的礼制思想及他的教育观点与当今教育的关联等诸方面。2017年11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纪念“朱张会讲”八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分发《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4]。总而言之,近些年有关张栻的研究十分活跃,他对道学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了更加广泛的认可。
数百年以来,有关张栻思想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他对朱熹思想的影响,而非其本身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关于他在修身方面的观点。儒家经典《中庸》强调的是在情感被激发之前,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恰当的程度进而达到的一种均衡、和谐的状态。[25]程颐提高了修身的要求,他要求弟子保存和守护这种感觉,就像他们在心中被唤起一样,并在心被表达之后,检验这种感觉。身处湖湘的张栻师法胡宏,认为“性”和“心”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他主张在行动中拓展认识,而不是关注于静坐和修身中提高涵养。[26]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受到杨时的影响,杨时在福建以二程学说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学说,主张在感觉被唤起前静坐冥想,不过朱熹对杨时的方法有所不满。因为仰慕张栻的学问,朱熹在1167年前往岳麓书院与其论学。两人当面论学,张栻说服朱熹将未发状态与“性”相联系,将已发状态与“心”相关联。朱熹回到福建之后,给张栻的四封信表明他接受了张栻的这一观点,但不久之后,朱熹就声明这四封信中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抱怨放弃了杨时静修沉思的方法后,自己在道德要求上有所下降。1169年他写信给张栻,宣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心的“体用”(实质和功能)。1172年他在《中和旧说》中的序言中,阐明了他思想的变化,以及怎样达到他所认为的正确中和观点的历程。[27]这一变化的取得一方面由于朱熹对闽学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在于他不但得益于湖湘学者的启发,而且还超越了湖湘学派,这标志着朱熹自信在思想的成熟和自己于道学中的权威方面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朱熹称张栻接受了这一新的思想体系,但是很难找到张栻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文献记载,因为朱熹在编纂张栻的文集时,并没有将张栻所有的书信和著作纳入其中。[28]
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同样也难以判断,他们有关重新解释“仁”一系列的讨论,试图纠正“仁”说陷于一偏的观点,特别是“二程”及其门人忽略“仁之爱”,过分地强调“仁之理”。几个世纪以来,朱熹对“仁”的终极定义——“爱之理”和“心之德”——一直为人所称道。相当一部分传统的和20世纪的学者断言张栻折服于朱熹的观点,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张栻最后完成的文章实际出自朱熹之手。[29尽管如此,刘述先(1934~2016)先生和田浩指出朱熹在其后与吕祖谦弟弟吕祖俭的书信中声明“心之德”的提法是张栻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起初遭到了朱熹的拒绝。[30]更重要的发现则源于陈来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张栻的《张子太极解义》,这本书说明了张拭在提升周敦颐(1017~1073)在道学中地位的重要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周敦颐地位的抬升一般被想当然地归于朱熹的功劳。[31]这些新的发现表明,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而言,近些年学界在张栻对朱熹的影响这一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二、吕祖谦与浙东学派
浙东(今属浙江)儒者与湖湘地区的儒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二程道学的两大分支——胡氏家族与吕氏家族之间的友谊。张九成(1092~1159)是联结这两个地区的另外一个纽带,他的心学观念对胡氏及吕氏家族皆有影响。[32]此外浙东与湖湘儒者都有着对国家强烈的使命感,而且他们都极力主张赶走占领中原腹地的女真人。因为吕氏家族从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末涌现了许多达官显贵和知名学者,这种家族的光环对吕祖谦的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带着吕氏家族对宋王朝的忠诚和乐观,他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编纂史学、制度方面的著作,以求更好地理解和改进治国之道。
吕氏家族长期以来以其博学,即精通中原文献而闻名,同时并不局限于师承一家的狭隘学派思想。就像蒋伟胜认为,吕家中原文献的藏书注重北宋特别是“二程”及张载(1020~1077)的著作,这也成为吕祖谦思想的核心观点。[33]因此吕祖谦非常自然地表达他治学方法(被牟宗三总结为“一元”论,被马恺之称为“有机”)[34]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将经典和历史、修身、政治及制度活动相结合。[35]他对道学早期思想家的贡献持认可态度,并试图保存他们著作的原貌,所以他曾批评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评点。[36]在此之前,他还为了维护胡宏的原本而反对朱熹修订、改变胡宏的《知言》。基于程颢、张九成、张栻对“心”的强调,吕祖谦直接通过“理”来分析“心”。与此相反朱熹关注程颐的“性即理”来建立他有关人性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心即是理。朱熹倾向把天理和人欲视作互相敌对的二元,吕祖谦认为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人的情感会寻求和谐甚至互相融合。因此吕祖谦在修身方法上更加倾向于张栻,即在行动中审视自己的实践,而不是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先冥想而后再实践。
吕祖谦认为修身应更多地在现实世界多加实践并学习“实学”,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浙东儒学一大特征。这种实学也运用了这样的口号“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和“切用于世”[37]。因为吕祖谦思想当中修身和实学互相融合,正如事功学、功利学说与朱熹的道学学说有某些互通之处一样,所以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38]
吕祖谦和朱熹主要的合作在于书院教育方面。田浩曾强调他们两人对书院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论及吕祖谦对朱熹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在朱熹从事书院教学之前,吕祖谦就有大量的门生,还有怎样发展书院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吕祖谦帮助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还为这座著名的宋代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朱熹为他的学生制定治学方向,并通过书院教学来提升其在经典解读及道学正统方面的权威地位,后来朱熹在这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在书院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快使其故去的友人黯然失色。
因为致力于治国之道的研究,吕祖谦将其大部分时间投身于研究古代和当时历史的演变,以求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从中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比如他曾告诫学生应该从历史中观察事物如何变化,而不是将历史只看作记忆中的大量历史事件。吕祖谦还对其门生提到,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该先停下来设身处地地考虑,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39]吕祖谦的许多史学著作是在讲学的同时完成的,比如他所作的《东莱博议》是为了指导学生如何在科举考试中写策论,可惜的是他的《大事记》只编到了公元前90年,在他病重直到去世前他都努力接续《左传》这一记录历史的传统。他的史学著作特别关注制度的发展,比如他的《历代制度详说》辑录了历代制度方面的史料。
吕祖谦和朱熹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些主要区别。朱熹特别注重经的地位,吕祖谦则认为经与史同等重要。同时他们两人都认为上古三代才是黄金时代,朱熹将天理和修身之道作为思想的准则,但吕祖谦更关注制度所产生的历史效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关注道德问题,吕祖谦则更注重制度因素。在评论历史学家方面,朱熹首先看他们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则较少关注史学家的个性,而是注重用历史来解释历史。朱熹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历史,而吕祖谦将天理融入到历史当中。[40]
在西方学界,马恺之(Kai Marchal)教授对吕祖谦的政治思想及其与朱熹的关系有最深入的研究。这两位道学家都认为通过个人修身进德提升儒家道德理想,进而可以从根本上促成社会和国家的变革。他们在社会和政治的道德楷模中,特别是从孟子及北宋儒家那里继承了自信。虽然两人都取法于儒家经典,相对于朱熹而言,吕祖谦更加主张儒家激进的政治改革。因此相较于吕祖谦而言,朱熹倾向于远离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而更倾向于提高个人及群体的道德修养。吕祖谦在其最后两年对政治上的挫败感到失望,所以如果他能像朱熹一样长寿的话,他对儒家道德能在根本上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观点也许也会有所动摇。尽管如此,有关儒家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主张成为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点。[41]这些分歧无疑反映了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然而这些也是他们两人思想差异的反映。
比如吕祖谦对王安石(1021~1086)的评价就比朱熹要积极得多,如他认为王安石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虽然吕祖谦也批评了王安石,但吕祖谦表达了一个和王安石相同的目标,马恺之总结为:“通过大规模的重组国家机构以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有为的政府以应对社会和政治上的挑战。”[42]吕祖谦对制度和史学的研究不但为改革提供了具体的理念和制度,还使他比道学阵营中大多数试图通过《周礼》中理想化的描述来恢复周朝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更加务实。比如在公元780年杨炎“两税法”的推行消除了在市场上购买土地的障碍后,恢复“井田制”的目标变得日益渺茫。但吕祖谦仍然很有信心,相信通过实际努力重建宗族谱系、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在社会上恢复由来已久的秩序和儒学家庭伦理。比如他曾写到虽然全面复兴古代制度风俗十分困难,但也有可能通过限制私有财产和保留地方武装开始逐步恢复。
马恺之也反驳一些现代学者对吕祖谦的批评,同时这也是对朱熹批评吕祖谦博杂和对最基本的道德概念关注不够的回应。比如朱熹同意一位门人对吕祖谦的描述:“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43]田浩曾指出朱熹对吕祖谦怀有敌意的批评几乎都始于这位好朋友去世之后。在和陈亮以及其他浙东儒者论辩的时候,朱熹认为这是吕祖谦错误的延续。[44]中国现在也有学者指出朱熹后来尖锐批评吕祖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追求道学权威并努力限制浙东学派的影响力。[45]
与包弼德教授将吕祖谦描述为“搞分门别类的书生”[46]不同,马恺之举例说明吕祖谦将自我修身与历史中的真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吕祖谦的许多研究关注探讨自我修身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了尽到士大夫的责任进而影响国家统治,他试图说服皇帝恢复传统的官僚集团以此作为对皇帝行为的制衡。但朱熹试图说服皇帝自愿限制自己的权力,吕祖谦则认识到通过制度限制皇权的必要性。皇权倾向于朱熹而非吕祖谦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朱熹主张关注皇帝内心道德的转变相比,吕祖谦通过制度来限制皇帝行为的方法看起来不合礼法并具有敌意。因此“与其他儒者思想家相比,吕祖谦较早地意识到‘道德的内化’的政治结果”[47]。
魏希德教授也曾对吕祖谦在1168年至1181年期间的道学领导地位提出质疑,她指出为什么吕祖谦没有像朱熹一样经常使用“道学”这一概念?[48]虽然他们在许多方面互相认同或合作,但我们应该了解他们两人的差别。除了其博学和善于综合各种治学方法外,吕祖谦比朱熹更早认识到道学群体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吕祖谦反映作为道学早期的社会政治联盟,其政治理想使得他们能够容忍相当多元的儒家思想。与此相反,朱熹特别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教化或思想的目的,所以他在使用“道学”来论述他的议题时要比吕祖谦更为严格。在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的密切关注反映了他对“醇儒”的认识,并努力清除道学内部被其他思想所影响的人。作为经典和传统的诠释者,朱熹重点关注思想的纯粹性及自己的权威地位,因此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探索思想意识纯粹性的过程中,朱熹较经常使用“道学”或“道统”等术语。朱熹的这种探索不但在其1181年对吕祖谦的悼词中宣称自己在道学中的领导地位中有所表现,而且在此后十年中他面对陈亮和陆九渊的挑战时显露无遗。
总之,虽然20世纪学者大多忽略了吕祖谦,但自从1992年开始学界在此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力地支持了田浩对吕祖谦在1168年到1181年之间是最重要思想家的评价。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吕祖谦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以及“主盟斯文”,他也是社会的精英、史学家和士大夫[49];二是他建立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基础,特别将心的修养与研究历史和经典相结合[50;三是他的博学并没有削弱他和张载及二程的思想渊源,此外他投身于修身[51];四是他作为道学家领袖并不受师承或某个派别的限制[52;五是吕祖谦对朱熹的重要影响在于其对经典的认识、书院教学和编纂《近思录》等,在宋代以后他对浙东地区的儒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53]
三、结语
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并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世纪和当代学者肯定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观念和贡献的一大因素在于地域的认同,不过将这种转变仅仅归为地域的认同未免过于片面。虽然除了直接驳斥其论点,中国学者鲜少提到外国学者的著述,但他们隐含地分享田浩的观点,也对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学家投以更多的关注。
本文是我参与撰写的由香港中文大学黄勇、吴启超两位教授主编的《朱熹哲学的指南》(The 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一书第十二章《朱熹与其同时代的儒家》(Zhu Xi's Contemporaries)的一部分。我之所以献上此文是因为一些参加岳麓书院会议的同人们也许会对这样一个面向西方公众的概述的例子感兴趣。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从与2016~2017年度来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的两位学者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玉敏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任仁仁及普渡大学历史系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的讨论中受益良多。任仁仁还为本次会议特将中文稿译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殷慧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帮忙修改译稿。在此谨向他们略表谢忱。
附注
注释:
[1]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页。
[2]同上注,第2页。
[3]同上注,第5页。
[4]同上注,第2页。
[5]同上注,第5页。
[6]同上注,第2页。
[7]同上注,第3页。
[8]同上注,第3~4页。
[9]同上注,第4页。
[10]同上。
[11]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页。
[12]同上。
[13]同上注,第6页。
[14]同上。
[15]同上注,第7~8页。
[16]同上注,第8页。
[17]同上。
[18]同上注,第9页。
[19]同上。
[20]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0页。
[21]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页。
[22]同上注,第9~10页。
参考文献:
〔1〕吕祖谦,《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2〕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原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注释:
[1]田浩,《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指向:新儒学与道学之间差异检讨》,载于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7~97页。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新儒学一词的使用:回应田浩教授》,载于伊沛霞(Patricia Ebrey)编、姚平译,《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英文版本:Hoyt Cleveland Tillman,“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Approaches to Examining Differences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eh(Daoxue)”,Philosophy East andWest 42.3,1992,pp.455~474.Wm.Theodore de Bary,“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A Response to Professor Tillma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3,1993,pp.541~555.
[2] Hilde De Weerdt,Competition over Content:Negotiating Standard for 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参看田浩《朱熹与道学的发展转化》,收入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载于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0页。
[4]蔡方鹿,《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
[5]朱汉民、陈谷嘉,《湖湘学派源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6]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7]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8]徐纪芳,《陆象山弟子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0年。
[9]英文名PhilosophyEastandWest,1992和1994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HoytCleveland Tillman,“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Approaches toExamin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eh(Daoxue)”,Philosophy EastandWest 42.3,1992,pp.455~474.Wm.Theodore de Bary,“TheUses of Neo-ConfuCianism:A Response to Professor Tillman”,Philosophy EastandWesT 43.3,1993,pp.541~555.
[1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11] Hans van Ess(叶翰),“Hu Hong's Philosophy”,inJohnMakeham(ed.),Dao Companion toNeo-Confucian 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p.110~115.
[12]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页。
[13]同上,第336页。
[14] Hoyt Cleveland 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is's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pp.30~36.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Hans van Ess,“Hu Hong'sPhilosophy”,in JohnMakeham(ed.),Dao Companionto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p.110~115.
[15] 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7页。
[16] Hoyt Cleveland Tillman,Christian Soffel,“Zhang Shi'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on Human Nature,Heart/Mind,Humanenes and the Supreme Ultimate”,in JohnMakeham(ed.),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126.
[17]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〇,《南轩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09页。
[18]邹锦良,《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西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9]向世陵,《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
[20]李可心,《由心的出入问题反思张拭之学的式微——兼明理学的内在展开与时代性》,载于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21]张栻撰,杨世文点校,《张栻集》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38页。
[22]如果要更多的解释,可以参看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7页。
[23]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24]任仁仁、顾宏义编撰,《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当时在长沙会议上分发的只是此书样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此书的日期为2018年1月22日。
[25] Christian,Soffel,Hoyt Cleveland Tillman,CUlTUr AlAuthority and PoliticalCulture inChina: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 Zhongyong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Jinand YuanDynasties,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2,p.42.中译本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26]苏铉盛,《张栻的中和说》,载于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27]陈来,《朱熹的<仁说>与宋代道学话语的演变》,载于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28]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Tillman andSoffel,“Zhang Shi'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Nature,Heart/Mind,Humanenes and the Supreme Ultimate”,in John Makeham(ed.),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
[29] Wing-tsit Chan,Chu Hsi:New Studi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翻译版:《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0]刘述先,《朱子的仁说、太极观点与道统问题的再审察》,《史学评论》,1983年第5期;Tillman,ConfucianDiscourseand Chu His s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 ofHawaii Press,1992,Chapter3;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章。
[31] 苏铉盛,《张栻的<太极解>》,载于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载于季羡林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32]刘玉敏,《心学源流:张九成心学与浙东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新勋,《张九成集前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33]蒋伟胜,《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考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2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1~21页。另参Marchal(马恺之),“Lü Zuqian's Political Philosophy”,John Makeham(ed.), Dao Companionto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202。
[35] Marchal,“Lü Zuqian's Political Philosophy”,John Makeham(ed.),DaoCompanionto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202.
[36] 吕祖谦撰,黄灵庚编,《吕祖谦全集》卷一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589页。另参Machal,“Lü Zuqian's Political Philosophy”,John Makeham(ed.),DaoCompanion to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202.
[37]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的实学思想述评》,《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38]蔡方鹿,《论吕祖谦的经世致用思想》,《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39]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四章。
[40]李同乐,《试论朱熹与吕祖谦历史观之异同》,《社科纵横》,2004年第9期。董平,《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41]Kai Marchal,Die Aufhebung des Politischen:LuZuqian(1137~1181)und derAufstieg des Neukon fuzianismus,Wei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1.
[42]Marchal,“Lü Zuqian's Political Philosophy”,John Makeham(ed.),DaoCompanion to 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209.
[4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9页。
[44]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五章。
[45]刘昭仁,《朱熹与吕祖谦的交谊》,《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6]Peter K.Bol(包弼德),“Reading Su Shi in Southern Song Wuzhou”,EastAsianLibraryJournal8.2,1998,pp.69~102.
[47]Marchal,“Lü Zuqian's Political Philosophy”,John Makeham(ed.),DaoCompaniontoNeo-Confucian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pp.212~218.
[48]Hilde De Weerdt(魏希德),“Review of Die Aufhebung des Politischen:Lü Zuqian(1137~1181)und der Aufstieg des Neukonfuzianismus”,by Kai Marchal,ChinaReviewInternational19.3,2012,pp.468~473,特别是第472页。
[49]潘富恩,《吕祖谦》,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50]杜海军,《谈吕祖谦浙东学术的领袖地位》,《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51]刘玉民,《南宋区域学术互动研究:以吕祖谦为中心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52]蒋伟胜:《合内外之道:吕祖谦哲学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
[53]程小青、郭丹,《吕祖谦与朱熹新理学》,《福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朱客座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荣退教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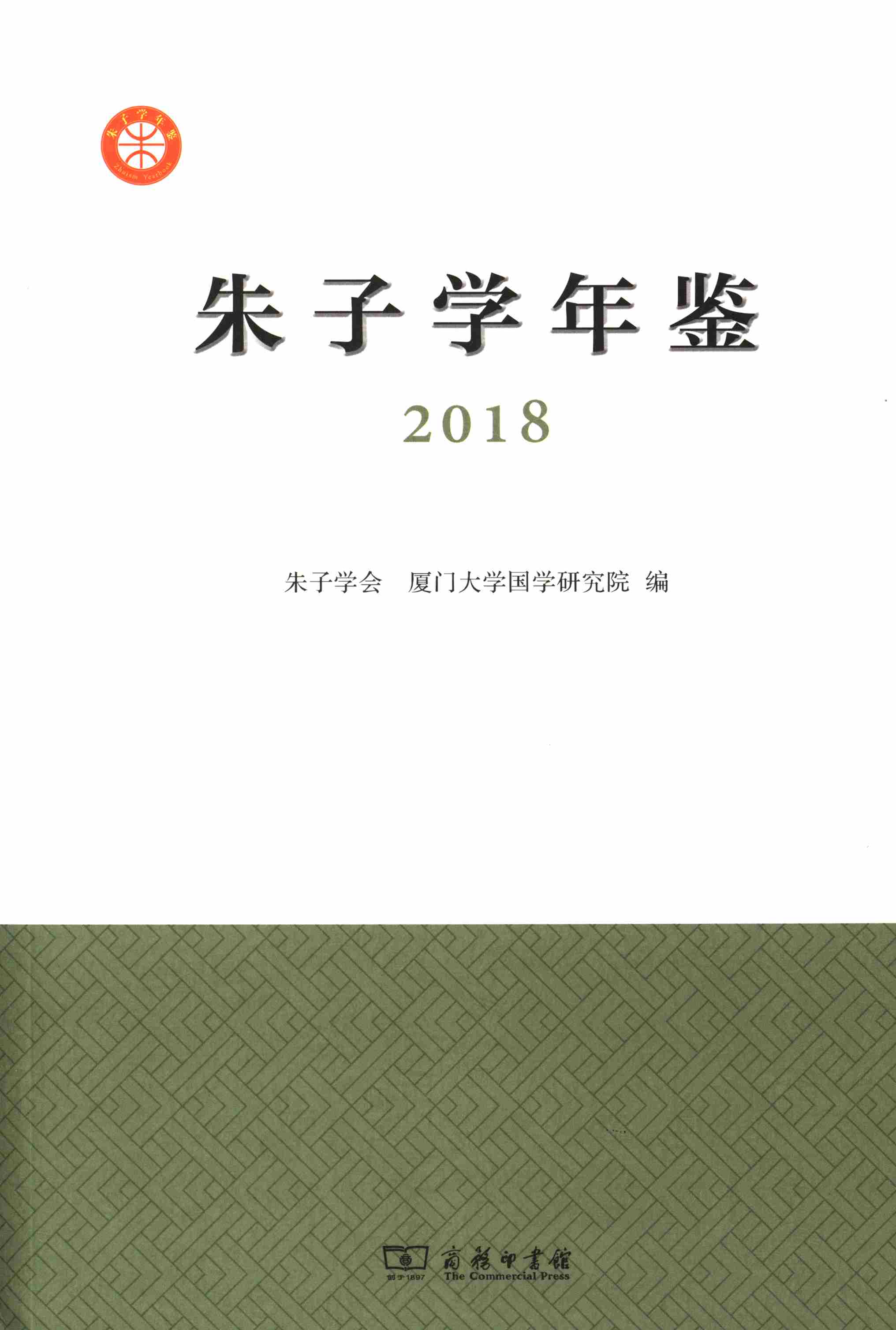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