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7》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120 |
| 颗粒名称: | 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96-21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建立了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吸收并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思想。他的思想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和史学等多个领域,其中理学与文学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相互影响渗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朱熹将经学义理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体现了这一点。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朱子学。 |
| 关键词: | 朱熹 思想家 理学思想 |
内容
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他吸收并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思想,从而建立了“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2]此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这些思想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朱熹的思想体系。虽然理学与文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为数众多的经学家兼治文学,文学家亦擅长经学,而经典本身又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文学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3]朱熹将经学义理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点。正如钱穆所说:“轻薄艺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应共赴之标的。”[4]因此,这里很有必要清理一下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或可为朱子学提供一个“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视野。
一、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研究
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两部著作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相关问题上。另外,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朱熹理学与其《韩文考异》关系的研究。
(一)理学与《诗集传》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诗经》彻底脱去了‘经典’的神圣皇袍,而被认作是一部诗歌总集。”[5]朱熹理学与《诗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地被学界所关注。1919年傅斯年提出:朱熹的《诗集传》虽然还有几分道气,但具有“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的特点。[6]1928年他在《泛论<诗经>学》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部书(《诗集传》)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7]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一书中认为:“朱熹论《诗》,如更进一步,超脱宗教性之经学,而立场于纯文学之观点,则一切新说适足以显其伟大的创见;奈其说仍局促于经学桎梏之下,仍以伦理的观念为中心,则何怪乎责难者之纷来。而吾人于此,亦可见经学与文学自有其不可混淆之封域矣。”[8]与此同时,郑振铎也认为,朱熹“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9]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多是点到为止,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港台学者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钱穆认为:“朱子以文学方法读《诗》,解脱了经学缠缚,而回归到理学家之义理。”[10]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主要集中在《诗集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是对“淫诗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义理时,涉及“淫诗”与义理及人情的关系,这与《诗经》的文学性相关。如谢谦说:“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沟通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淫诗’之说能够在经学范围内成为可以‘自圆其说’的体系。严格说来,朱熹不是发现了《诗经》中有‘淫诗’,而是从理学角度完整地阐述了‘淫诗’为教的经学意义。”[11]认为朱熹将“淫诗”纳入了他的理学体系来阐述他的诗教思想。另外,赵沛霖、吴正岚、谢海林等对此也持相似的观点。[12以上学者认为,朱熹的《诗经》研究虽然涉及“淫诗”这一文学性的特点,但本质上朱熹是站在理学的角度来阐释《诗经》的。台湾学者姜龙翔亦云:“朱子对淫奔诗的界定虽是由其理学思想出发,否定诗人情性,进而对于民歌抒发自由情感的本质有所误解,但经由朱子的论述,却较汉学将《诗经》视为国史代言创作的产生论,表现出多元的解释。”[13台湾学者黄景进从朱熹的心性哲学出发做了研究,说:“朱子根据其心性哲学,认为情有善有不善,故诗亦有正有变,由此认定《诗经》中有‘淫诗’(淫诗所表达的是不正的感情),并反对‘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说法。”[14]
二是认为朱熹以文学解《诗》,突破了理学的束缚。美籍学者杜维明在《朱子解诗》中说:“朱熹把《诗经》视为美学思想的源泉和道德训诫的宝藏而加以认真研究。……朱熹认为在客观地分析诗以前必须朗读诗和体验诗的意境。”[15]这也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读《诗经》。莫砺锋认为:“朱熹著《诗集传》,其本意也是从事经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悟性,其治学态度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所以他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质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诗集传》在实际上终于打破了经学的藩篱,《诗经》学终于在一位理学宗师的手中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16]汪大白说:“朱熹正是在他的理学宗旨与文学意识紧密结合和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研究直接影响并实际革新了旧的经学研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诗经》学发展史的根本性转变。”[17]另外,檀作文、李士金也对此发表了相似的论述。[18]以上学者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理学思想的过程中,“以《诗》言《诗》”从而促进了《诗经》文学性的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朱熹研究《诗经》的方法是分不开的。蔡方鹿以朱熹的读书法为切入点,认为:“‘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文学的功能在于抒情,诗人言《诗》,则‘发乎情’;其理学的要旨则在于阐发义理,理学家说《诗》,不离理与性善。朱熹既重《诗》文之言情的本义,又重义理的阐发,因此可以说,朱熹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情与理、情与性的结合。”[19]并指出:“朱熹客观地看到古人作《诗》是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突出一个‘情’字,认为抒发感情和自然情感是诗人作《诗》的本意。同时,朱熹也注意把吟咏情性与玩味义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20]分析了文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郝永以《二南》为例分析了朱熹二《南》解释学中“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矛盾性”。[21]]台湾学者陈昭瑛则“尝试建构朱子的诗学及其与儒家诗学的关系”,“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脉络来掌握朱子诗学与儒家诗学的现代意义。”[22]
三是把朱熹的《诗经》学与经典解释学结合起来。邹其昌从诠释学美学思想的角度认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由‘以《诗》说《诗》’所开启,历经‘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之磨炼,旨在获得‘性情中和’之境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转折意义的典范。诗经诠释学由此逐渐走出‘经学’,走向真正的审美!”[23]即朱熹在对《诗经》的诠释中认识到了其中的文学性。曹海东认为:“就朱熹的经典解释活动看,他可以说是很好地践行了上述解释学原则。对《诗经》的解释就是一个显证。”[24]这些原则包括据诗之情实自出新解,把训诂释文义与讽诵见道理相结合,即在《诗经》诠释中,把文学与理学结合起来。郝永则系统地对朱熹《诗经》的解释学进行了研究。说:“朱熹解释《诗经》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其文学特质的重视,二是对其理学价值的发掘。两者都是对汉唐经学以美刺解《诗经》的大突破、大发展。”“故朱熹的《诗经》解释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既有文学的维度,也有理学和史学的维度;既是对经学旧说的继承与扬弃,也有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总之,朱熹《诗经》解释学是以理学为旨归的多维度的经学体系。”[25]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一角度对朱熹的《诗经》学进行研究,我们要清楚的是,理学与文学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的分类下产生的,“然若从贴近古代情状的视角观察,从前儒者的经典诠释活动,也可能透过类同文艺批评的形态发生,特别是在向以艺术性见称的《诗经》身上,朱熹的《诗集传》或者就是个典型案例。”[26]因此,我们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不能割裂其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应从理学、文学二元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和把握朱熹的《诗经》研究中理学与文学间相分相合、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理学与《楚辞集注》
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其著作《楚辞集注》一书中,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朱熹的《楚辞集注》展开。朱熹的楚辞学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有学者认为:“朱熹最早彻底地以文学眼光看待楚辞,他自觉抛弃了楚辞研究中的经学标准,抓住了楚辞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27]也有学者认为:“朱熹在鉴赏楚辞的时候,的确是把‘情’字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只要理智稍胜感情,便要流露他道学面孔,立刻会对情字加以限定词,要求情必须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28]实际上,朱熹的楚辞研究并没有抛弃经学、理学的标准,这一点学界多有讨论。韩国学者朴永焕认为:“朱熹在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理论基础上,主张实行以道为本的判文、以理为准的评诗、以古为法的复古思想。”[29]并且这些文学思想强烈地影响了《楚辞》的研究。束景南也认为朱熹在注解《楚辞》时“用理学的‘文化范型’重新铸造屈原的历史形象”并“把作为游艺之学的文学也拉回到理学的轨道与框架中去。”[30]孙光从篇目选择和体例确定、文本注释、屈原思想的阐发、楚辞艺术的观照、注释特点五个方面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的关系。他认为:“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使其在注释中既遵循理学价值标准阐发义理,又能够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31]罗敏中从朱熹的“尊屈倾向”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32]李士金则研究了朱熹将理学思想引入楚辞研究的原因,认为:“朱熹把他的理学思想引入《楚辞集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南宋科技水平进步之结果。”33另外,还有学者对朱熹的辞赋观做了研究。何新文认为:朱熹的辞赋批评“明显具有以道德哲学标准否定文学的偏见。”[34]这在注释篇目的选取上也有体现。莫砺锋认为《楚辞后语》对作品的选择受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理学家的迂腐性。[35]于浴贤、徐涓、台湾的梁升勋对此也做了考察。[36]虽然以理学的标准来选取篇目确实会遗漏一些好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就此来研究朱熹的辞赋观和文学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学者,多从朱熹的理学思想出发来论述理学对朱熹楚辞学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理学阐释方法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肖伟光认为:“《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37]徐涓从格物致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格物’结果是‘物格’与‘知至’,亦即求得事物义理之豁然贯通,对《楚辞》而言,就是兼得其‘性情’与‘义理’。”[38]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集注》及楚辞学关系的研究多从理学对楚辞学的影响着手,而很少注意到《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对于朱熹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朱熹在评价《楚辞》时多是义理性与文学性兼有的。如据《楚辞集注》载:“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39在这里,朱熹把阐发君臣之义理建立在承认《楚辞》“陈情”感怀之言情性的基础上,可见文学对理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朱熹《楚辞》学的研究,不能忘记朱熹理学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和朱熹《楚辞》研究理学与文学兼顾的特点,应从理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入手,找出二者的联系。
(三)理学与《韩文考异》
对于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的研究,学者们多把《韩文考异》当作朱熹校勘学的代表而研究其校勘学意义。吴长庚认为:“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法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40]朱熹的《韩文考异》中确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但朱熹并不是为了校勘而校勘,他是借助韩文的校勘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的。正如钱穆所说:“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然则校勘虽小业,于义理经术史学文章靡不有其相关互涉之处。后人仅知从事校勘,又何能望其津涯,而窥其底蕴。”[41]可见,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束景南认为:“朱熹在党锢中选择韩愈文集做考异的目的又不仅是为了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个大文豪的威望来巧妙宣扬‘道学’的深意。贯串在《考异》中对韩愈批判的一面,便渗透了他的道学‘伪气’。”[42]
二、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研究
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有文道观、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等四个主要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如蔡方鹿、王哲平等。蔡方鹿认为:“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道合一,‘即文以讲道’和诗理结合的思想。其理学与文学并行不相悖,可以互相结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与只重理学而轻视文学的理学家相异,同时也表明理学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文学的桎梏,尽管理学有抑制文学的倾向。”[43王哲平从文学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做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44]李春强则从理学著作《论语集注》出发综合研究了朱熹的文学本体观、创作观等文学理论。[45]
(一)文道观
张立文指出:“文道关系论是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文道关系论的展现,便是诗与理的关系。”[46]台湾学者杨儒宾也认为“朱子说‘道之显者谓之文’,‘文’与‘道’可视为一体的表里关系,这当视为理学家另一种对文学重要的界定。”[47]可见,朱熹文道观也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对于这一论题,学界的主要看法是“文以载道”或“文道合一”。“文以载道”论以周予同为代表。他说:“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亦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如皮附以今日流行之文学术语,则朱熹或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48]此外,朱东润、陈千帆、台湾学者张健、钱穆等都持相近的观点。[49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持“文道合一”论,他认为:“文学不是‘道’的从属物,而是持有自身根据的自立之物。文学存在着自律性,植基于‘气’(气象)的发动,在这种根源性中文与道合成一体。”[50]吴长庚认为:“文道合一是建立在文与道二者并重,各不偏废的基础上,并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总结。”[51]对此莫砺锋、吴法源也持相同的观点。[52束景南进一步认为:“朱熹通过曾巩融合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学问路数,统一了道统与文统。”[53]值得一提的是,程刚从“理为太极”的太极观出发来讨论朱熹的文学本原论,认为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本论的哲学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一方面延续了文从道出的本原论,以文为工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于程颐‘作文害道’的一个修正。”[54]
(二)理学与诗论
郭绍虞指出:“朱子论诗不唯集道学家之大成,也且兼诗人之诗论而有之了。”[55]对于朱熹理学与诗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理学思想对其诗论的影响上。一般认为,朱熹诗论的基础态度是“道学是第一义的当行职责,做诗是第二义的感情辅助”,“诗歌的首要第一条便是义理纯正,所谓‘诗以道性情之正’。”[56]马积高亦认为,朱熹的诗论“强调诗人的主观动机要合于所谓‘性情之正’才行。”[57]以上学者的观点都看到了理学对于朱熹诗论的影响。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进一步认为:朱熹“以儒家心性理论为基础的诗歌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要求诗歌创作将情感体验与性理规范统一起来,成为作者道德人格和高远胸襟的流露,具自然平淡的‘中和’之美。”[58]石明庆讨论了朱熹理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影响其诗学的主要有理本气具的理气论、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居敬穷理的工夫论,以及心与理一的境界论等理学思想。”[59]另外,台湾学者黄景进从美学的角度对朱熹诗论进行了研究。他说:“大体而言,当朱子在论《诗经》时,他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发挥儒家传统的诗教观为目的;而当他在评论历代的诗人时,却较注意诗人在美学方面的表现。”[60]
以上学者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楚朱熹理学思想影响下的诗学理论。这也启发我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评价朱熹诗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宋代理学家诗论中最有价值的”,“他论诗的许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珍视,其保守的一面则应予以扬弃。”[6[
(三)理学与古文理论
对于朱熹理学与古文理论关系的研究,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台湾学者何寄澎认为朱熹文论的“一切观点(包括文学性的观点)悉以道学为归趋。见证了朱子文论一方面是更道学化的;一方面却又是更包容而圆融的。”[62]闵泽平认为:“朱熹的文章理论虽带有浓厚的道学色彩,其间却颇多精辟的见解。他也重道轻文,但其观念远比周、程等人通达。”[63]
(四)理学与作家作品批评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除以上三个方面外,也有学者对朱熹的作家作品批评进行了研究。如踪凡认为:“朱熹论两汉诗赋,手中拿着两大标尺:一曰道德,二曰真实……他由此出发而得出的扬贾抑马,尤其是贬斥扬雄的结论尤其让人不能信服。”[64]全华凌论述了朱熹以“道”来评价韩文的得失。[65]黄炳辉认为朱熹的唐诗批评其精辟处在于道学和文学的统一,其瑕疵处“是以道学家的眼光代替诗艺术本身的观察。”[66]莫砺锋对朱熹的作家人品批评做了研究。认为:“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极为关注作家的品德修养。”[67]李士金则对此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朱熹“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68]谢谦全面地考查了朱熹的文学批评,他说:“朱熹正是根据这一新的价值标准,对《诗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的阐释与评价,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批评的模式。这个‘以理说诗’的道德批评模式同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史证诗’的历史批评模式一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69]以上学者研究的多是朱熹理学对某一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虽然不乏深刻的论述,但却缺乏系统性。另外,学者们多关注的是朱熹理学对其文论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文学理论是他理学思想的反映,及朱熹文学思想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在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某一文学理论,较少系统地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很少讨论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作为朱熹文学思想基础的文道观对他的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
三、朱熹理学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
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之史学与文学》一文中指出:“朱熹之文学作品,诗赋散文,各体均有。然韵文喜插入说理之语,每使人深感酸腐之气……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70]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诗歌与文章创作两个方面。
对于朱熹诗歌创作的研究集中在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上。胡明认为:“朱熹作为一个道学家,他的诗却绝少道学气,更无头巾气、酸馅气。”71郭齐认为:“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72]许总对朱熹的创作实践做了分析,认为:朱熹的创作实践“即使是为了说明治学之理,亦全借优美的自然意象表达出来。正因这类‘不腐之作’,朱熹诗被后人称为‘道学中之最活泼者’”[73]。莫砺锋亦认为:“朱熹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丰富生活情趣的诗人,这种独特的素质使他成功地消除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并进而使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74]李育富研究了朱熹易学思想与其诗歌关系的互动,说:“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75]吴长庚则“从朱熹解易解诗之思维程序、方法、原则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朱熹的解诗思维中,他致力于诗歌比兴形象的发掘,寻求诗歌感发性情的活的功能,力求通过正确的诗解,建立一套开放性的解诗思维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易解思维中之积极成分的”。[76]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朱熹诗中的理学思想。美籍学者陈荣捷在《论朱子<观书有感>诗》一文中解释了诗中词语的理学含义。[77韩国学者李秀雄认为:“朱熹作诗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诗本身的艺术形象。他使诗中的理和趣互相和谐而达到交融的境界。”[78]日本学者申美子在《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朱子数量庞大的诗作,正是研究其一生思想形成、转变、发展极其丰富而真确的材料”,并从朱熹的诗作出发,“探讨其一生学问思想的发展轨迹”。[79]石明庆也认为,朱熹的诗歌“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80]。在朱杰人看来,“朱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抑或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对宋代的诗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公正的、充分的估价”[81]。胡迎建亦云:“了解其理学与诗歌的关系,有利于理解其诗。”[82]这同样也能进一步了解朱熹的理学思想。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章创作关系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饶宗颐对朱熹的文章做了研究,认为“朱子说理之文,逻辑性特强,又覃思者久,增、减不得,极得洗伐工夫”[83]。莫砺锋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他(朱熹)的散文写得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他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理解理学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窗口”[84。而闵泽平则深入地探讨了朱熹理学与其文章创作的关系,认为“朱熹行文的从容、平和,首先来自于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对义理的体认与把握,来自他道学气象的自然流露”[85。方笑一将朱熹的经学与文章之学相结合,认为:“与北宋儒者不同,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86另外,王仕强认为:朱熹“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87]具有典范意义。黄拔荆、周旻则“分析了朱词与其文学观、理学观的关系”[88]。许总则对朱熹理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说:“朱熹将‘义理’与‘诗文’加以遘合,表明了对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89]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明了理学对朱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以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的朱熹的文学作品。另外,通过分析研究朱熹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究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理学与文学是怎样融合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这也是朱熹文学作品对于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特殊意义。
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展望
通过以上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是开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学与《诗经》学、文道观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但研究成果多为简要的概括式论述,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港台及海外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虽然百年来学术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以至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比较而言,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进行,尚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做出一个融会贯通、整体综合性的系统研究。由于朱熹思想本身就是由文、史、哲,儒、佛、道等相互贯通而构成,朱熹理学与文学是统一于朱熹思想的一个整体。因此,研究朱熹理学不及文学、研究朱熹文学不及理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一些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某一方面的文学做过个案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作为整体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故未能揭示出朱熹理学与文学之总体特征,因此也不能进一步说明朱熹理学与文学之关系。所以目前的研究情况与朱熹既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尽管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目前的研究,确实是朱子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需要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高。在这个新的视域下,去挖掘朱熹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实质及所体现的朱子学的特点,而不是以往大多就事论事地分论朱熹的理学和文学,从而澄清和阐明朱熹理学思想中的文学性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回答其理学怎么通过其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而其理学思想里又具有哪些其他理学家不曾有的文学性等问题?从而客观揭示朱熹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及情理结合的特征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既对深入研究朱熹理学有利,也对深入研究朱熹文学有利,更对全面、综合研究朱子学有利。因此,站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朱熹思想及其价值、地位和影响,对于学术界完整理解朱熹的整个思想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我们以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为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进而展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开展:
(一)朱熹思想是在致广大、尽精微,涵盖、吸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打破界限,以融会贯通的视角去研究朱熹思想。这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学科学术研究之间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时代要求。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将朱熹的理学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仅以此促进朱子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而且拓宽了研究领域,这对朱子学的研究很有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应将具体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由于朱熹文学是由《诗经》学、楚辞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等多方面构成,我们应以这些具体的研究为基础,运用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散到联系、从局部到整体的观点和思路,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展开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并加以概括提炼,从而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系统的认识,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文化史上伦理与自然之争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尚伦理、重教化与崇自然、重情感两种文化价值观之争,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对其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其理学思想中的尚伦理、重教化与文学思想中崇自然、重情感是怎么统一于朱熹思想中的,它们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的融合又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研究的展开将为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创新的视角,同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儒学与文学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及所体现的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亦是朱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所要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某一学科的创新。某一理论学科的成就,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先导。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应采用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融合互动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上,应采取点、面、线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置于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以朱熹理学与文学为点,以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和盛行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为面,以整个中国经学史、文学史、理学史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结合,在相互联系中,做纵横比较,分析探讨,深稽博考,融会贯通,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在中国经学史与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和作用。
(四)在研究工作中,应将理论分析与训诂相结合。既要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把研究建立在考证、训诂、细读深研文本,弄清掌握朱熹经学、文学著作本义的基础上,又要避免单纯的训诂考证,而忽视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及其思想性的深入、深刻表达。
以上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仅是我们的一点意见。希望通过以上的评述和论析,在以往研究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拓展,站在朱子学促进、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时代高度,以创新的方法、理论和新视野、新材料的挖掘运用,为朱子学的研究,在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影响、结合的视域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展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研究
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两部著作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相关问题上。另外,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朱熹理学与其《韩文考异》关系的研究。
(一)理学与《诗集传》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诗经》彻底脱去了‘经典’的神圣皇袍,而被认作是一部诗歌总集。”[5]朱熹理学与《诗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地被学界所关注。1919年傅斯年提出:朱熹的《诗集传》虽然还有几分道气,但具有“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的特点。[6]1928年他在《泛论<诗经>学》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部书(《诗集传》)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7]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一书中认为:“朱熹论《诗》,如更进一步,超脱宗教性之经学,而立场于纯文学之观点,则一切新说适足以显其伟大的创见;奈其说仍局促于经学桎梏之下,仍以伦理的观念为中心,则何怪乎责难者之纷来。而吾人于此,亦可见经学与文学自有其不可混淆之封域矣。”[8]与此同时,郑振铎也认为,朱熹“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9]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多是点到为止,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港台学者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钱穆认为:“朱子以文学方法读《诗》,解脱了经学缠缚,而回归到理学家之义理。”[10]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主要集中在《诗集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是对“淫诗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义理时,涉及“淫诗”与义理及人情的关系,这与《诗经》的文学性相关。如谢谦说:“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沟通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淫诗’之说能够在经学范围内成为可以‘自圆其说’的体系。严格说来,朱熹不是发现了《诗经》中有‘淫诗’,而是从理学角度完整地阐述了‘淫诗’为教的经学意义。”[11]认为朱熹将“淫诗”纳入了他的理学体系来阐述他的诗教思想。另外,赵沛霖、吴正岚、谢海林等对此也持相似的观点。[12以上学者认为,朱熹的《诗经》研究虽然涉及“淫诗”这一文学性的特点,但本质上朱熹是站在理学的角度来阐释《诗经》的。台湾学者姜龙翔亦云:“朱子对淫奔诗的界定虽是由其理学思想出发,否定诗人情性,进而对于民歌抒发自由情感的本质有所误解,但经由朱子的论述,却较汉学将《诗经》视为国史代言创作的产生论,表现出多元的解释。”[13台湾学者黄景进从朱熹的心性哲学出发做了研究,说:“朱子根据其心性哲学,认为情有善有不善,故诗亦有正有变,由此认定《诗经》中有‘淫诗’(淫诗所表达的是不正的感情),并反对‘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说法。”[14]
二是认为朱熹以文学解《诗》,突破了理学的束缚。美籍学者杜维明在《朱子解诗》中说:“朱熹把《诗经》视为美学思想的源泉和道德训诫的宝藏而加以认真研究。……朱熹认为在客观地分析诗以前必须朗读诗和体验诗的意境。”[15]这也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读《诗经》。莫砺锋认为:“朱熹著《诗集传》,其本意也是从事经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悟性,其治学态度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所以他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质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诗集传》在实际上终于打破了经学的藩篱,《诗经》学终于在一位理学宗师的手中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16]汪大白说:“朱熹正是在他的理学宗旨与文学意识紧密结合和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研究直接影响并实际革新了旧的经学研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诗经》学发展史的根本性转变。”[17]另外,檀作文、李士金也对此发表了相似的论述。[18]以上学者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理学思想的过程中,“以《诗》言《诗》”从而促进了《诗经》文学性的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朱熹研究《诗经》的方法是分不开的。蔡方鹿以朱熹的读书法为切入点,认为:“‘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文学的功能在于抒情,诗人言《诗》,则‘发乎情’;其理学的要旨则在于阐发义理,理学家说《诗》,不离理与性善。朱熹既重《诗》文之言情的本义,又重义理的阐发,因此可以说,朱熹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情与理、情与性的结合。”[19]并指出:“朱熹客观地看到古人作《诗》是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突出一个‘情’字,认为抒发感情和自然情感是诗人作《诗》的本意。同时,朱熹也注意把吟咏情性与玩味义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20]分析了文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郝永以《二南》为例分析了朱熹二《南》解释学中“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矛盾性”。[21]]台湾学者陈昭瑛则“尝试建构朱子的诗学及其与儒家诗学的关系”,“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脉络来掌握朱子诗学与儒家诗学的现代意义。”[22]
三是把朱熹的《诗经》学与经典解释学结合起来。邹其昌从诠释学美学思想的角度认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由‘以《诗》说《诗》’所开启,历经‘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之磨炼,旨在获得‘性情中和’之境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转折意义的典范。诗经诠释学由此逐渐走出‘经学’,走向真正的审美!”[23]即朱熹在对《诗经》的诠释中认识到了其中的文学性。曹海东认为:“就朱熹的经典解释活动看,他可以说是很好地践行了上述解释学原则。对《诗经》的解释就是一个显证。”[24]这些原则包括据诗之情实自出新解,把训诂释文义与讽诵见道理相结合,即在《诗经》诠释中,把文学与理学结合起来。郝永则系统地对朱熹《诗经》的解释学进行了研究。说:“朱熹解释《诗经》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其文学特质的重视,二是对其理学价值的发掘。两者都是对汉唐经学以美刺解《诗经》的大突破、大发展。”“故朱熹的《诗经》解释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既有文学的维度,也有理学和史学的维度;既是对经学旧说的继承与扬弃,也有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总之,朱熹《诗经》解释学是以理学为旨归的多维度的经学体系。”[25]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一角度对朱熹的《诗经》学进行研究,我们要清楚的是,理学与文学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的分类下产生的,“然若从贴近古代情状的视角观察,从前儒者的经典诠释活动,也可能透过类同文艺批评的形态发生,特别是在向以艺术性见称的《诗经》身上,朱熹的《诗集传》或者就是个典型案例。”[26]因此,我们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不能割裂其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应从理学、文学二元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和把握朱熹的《诗经》研究中理学与文学间相分相合、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理学与《楚辞集注》
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其著作《楚辞集注》一书中,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朱熹的《楚辞集注》展开。朱熹的楚辞学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有学者认为:“朱熹最早彻底地以文学眼光看待楚辞,他自觉抛弃了楚辞研究中的经学标准,抓住了楚辞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27]也有学者认为:“朱熹在鉴赏楚辞的时候,的确是把‘情’字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只要理智稍胜感情,便要流露他道学面孔,立刻会对情字加以限定词,要求情必须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28]实际上,朱熹的楚辞研究并没有抛弃经学、理学的标准,这一点学界多有讨论。韩国学者朴永焕认为:“朱熹在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理论基础上,主张实行以道为本的判文、以理为准的评诗、以古为法的复古思想。”[29]并且这些文学思想强烈地影响了《楚辞》的研究。束景南也认为朱熹在注解《楚辞》时“用理学的‘文化范型’重新铸造屈原的历史形象”并“把作为游艺之学的文学也拉回到理学的轨道与框架中去。”[30]孙光从篇目选择和体例确定、文本注释、屈原思想的阐发、楚辞艺术的观照、注释特点五个方面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的关系。他认为:“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使其在注释中既遵循理学价值标准阐发义理,又能够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31]罗敏中从朱熹的“尊屈倾向”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32]李士金则研究了朱熹将理学思想引入楚辞研究的原因,认为:“朱熹把他的理学思想引入《楚辞集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南宋科技水平进步之结果。”33另外,还有学者对朱熹的辞赋观做了研究。何新文认为:朱熹的辞赋批评“明显具有以道德哲学标准否定文学的偏见。”[34]这在注释篇目的选取上也有体现。莫砺锋认为《楚辞后语》对作品的选择受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理学家的迂腐性。[35]于浴贤、徐涓、台湾的梁升勋对此也做了考察。[36]虽然以理学的标准来选取篇目确实会遗漏一些好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就此来研究朱熹的辞赋观和文学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学者,多从朱熹的理学思想出发来论述理学对朱熹楚辞学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理学阐释方法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肖伟光认为:“《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37]徐涓从格物致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格物’结果是‘物格’与‘知至’,亦即求得事物义理之豁然贯通,对《楚辞》而言,就是兼得其‘性情’与‘义理’。”[38]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集注》及楚辞学关系的研究多从理学对楚辞学的影响着手,而很少注意到《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对于朱熹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朱熹在评价《楚辞》时多是义理性与文学性兼有的。如据《楚辞集注》载:“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39在这里,朱熹把阐发君臣之义理建立在承认《楚辞》“陈情”感怀之言情性的基础上,可见文学对理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朱熹《楚辞》学的研究,不能忘记朱熹理学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和朱熹《楚辞》研究理学与文学兼顾的特点,应从理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入手,找出二者的联系。
(三)理学与《韩文考异》
对于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的研究,学者们多把《韩文考异》当作朱熹校勘学的代表而研究其校勘学意义。吴长庚认为:“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法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40]朱熹的《韩文考异》中确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但朱熹并不是为了校勘而校勘,他是借助韩文的校勘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的。正如钱穆所说:“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然则校勘虽小业,于义理经术史学文章靡不有其相关互涉之处。后人仅知从事校勘,又何能望其津涯,而窥其底蕴。”[41]可见,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束景南认为:“朱熹在党锢中选择韩愈文集做考异的目的又不仅是为了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个大文豪的威望来巧妙宣扬‘道学’的深意。贯串在《考异》中对韩愈批判的一面,便渗透了他的道学‘伪气’。”[42]
二、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研究
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有文道观、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等四个主要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如蔡方鹿、王哲平等。蔡方鹿认为:“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道合一,‘即文以讲道’和诗理结合的思想。其理学与文学并行不相悖,可以互相结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与只重理学而轻视文学的理学家相异,同时也表明理学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文学的桎梏,尽管理学有抑制文学的倾向。”[43王哲平从文学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做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44]李春强则从理学著作《论语集注》出发综合研究了朱熹的文学本体观、创作观等文学理论。[45]
(一)文道观
张立文指出:“文道关系论是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文道关系论的展现,便是诗与理的关系。”[46]台湾学者杨儒宾也认为“朱子说‘道之显者谓之文’,‘文’与‘道’可视为一体的表里关系,这当视为理学家另一种对文学重要的界定。”[47]可见,朱熹文道观也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对于这一论题,学界的主要看法是“文以载道”或“文道合一”。“文以载道”论以周予同为代表。他说:“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亦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如皮附以今日流行之文学术语,则朱熹或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48]此外,朱东润、陈千帆、台湾学者张健、钱穆等都持相近的观点。[49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持“文道合一”论,他认为:“文学不是‘道’的从属物,而是持有自身根据的自立之物。文学存在着自律性,植基于‘气’(气象)的发动,在这种根源性中文与道合成一体。”[50]吴长庚认为:“文道合一是建立在文与道二者并重,各不偏废的基础上,并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总结。”[51]对此莫砺锋、吴法源也持相同的观点。[52束景南进一步认为:“朱熹通过曾巩融合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学问路数,统一了道统与文统。”[53]值得一提的是,程刚从“理为太极”的太极观出发来讨论朱熹的文学本原论,认为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本论的哲学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一方面延续了文从道出的本原论,以文为工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于程颐‘作文害道’的一个修正。”[54]
(二)理学与诗论
郭绍虞指出:“朱子论诗不唯集道学家之大成,也且兼诗人之诗论而有之了。”[55]对于朱熹理学与诗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理学思想对其诗论的影响上。一般认为,朱熹诗论的基础态度是“道学是第一义的当行职责,做诗是第二义的感情辅助”,“诗歌的首要第一条便是义理纯正,所谓‘诗以道性情之正’。”[56]马积高亦认为,朱熹的诗论“强调诗人的主观动机要合于所谓‘性情之正’才行。”[57]以上学者的观点都看到了理学对于朱熹诗论的影响。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进一步认为:朱熹“以儒家心性理论为基础的诗歌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要求诗歌创作将情感体验与性理规范统一起来,成为作者道德人格和高远胸襟的流露,具自然平淡的‘中和’之美。”[58]石明庆讨论了朱熹理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影响其诗学的主要有理本气具的理气论、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居敬穷理的工夫论,以及心与理一的境界论等理学思想。”[59]另外,台湾学者黄景进从美学的角度对朱熹诗论进行了研究。他说:“大体而言,当朱子在论《诗经》时,他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发挥儒家传统的诗教观为目的;而当他在评论历代的诗人时,却较注意诗人在美学方面的表现。”[60]
以上学者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楚朱熹理学思想影响下的诗学理论。这也启发我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评价朱熹诗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宋代理学家诗论中最有价值的”,“他论诗的许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珍视,其保守的一面则应予以扬弃。”[6[
(三)理学与古文理论
对于朱熹理学与古文理论关系的研究,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台湾学者何寄澎认为朱熹文论的“一切观点(包括文学性的观点)悉以道学为归趋。见证了朱子文论一方面是更道学化的;一方面却又是更包容而圆融的。”[62]闵泽平认为:“朱熹的文章理论虽带有浓厚的道学色彩,其间却颇多精辟的见解。他也重道轻文,但其观念远比周、程等人通达。”[63]
(四)理学与作家作品批评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除以上三个方面外,也有学者对朱熹的作家作品批评进行了研究。如踪凡认为:“朱熹论两汉诗赋,手中拿着两大标尺:一曰道德,二曰真实……他由此出发而得出的扬贾抑马,尤其是贬斥扬雄的结论尤其让人不能信服。”[64]全华凌论述了朱熹以“道”来评价韩文的得失。[65]黄炳辉认为朱熹的唐诗批评其精辟处在于道学和文学的统一,其瑕疵处“是以道学家的眼光代替诗艺术本身的观察。”[66]莫砺锋对朱熹的作家人品批评做了研究。认为:“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极为关注作家的品德修养。”[67]李士金则对此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朱熹“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68]谢谦全面地考查了朱熹的文学批评,他说:“朱熹正是根据这一新的价值标准,对《诗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的阐释与评价,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批评的模式。这个‘以理说诗’的道德批评模式同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史证诗’的历史批评模式一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69]以上学者研究的多是朱熹理学对某一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虽然不乏深刻的论述,但却缺乏系统性。另外,学者们多关注的是朱熹理学对其文论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文学理论是他理学思想的反映,及朱熹文学思想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在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某一文学理论,较少系统地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很少讨论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作为朱熹文学思想基础的文道观对他的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
三、朱熹理学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
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之史学与文学》一文中指出:“朱熹之文学作品,诗赋散文,各体均有。然韵文喜插入说理之语,每使人深感酸腐之气……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70]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诗歌与文章创作两个方面。
对于朱熹诗歌创作的研究集中在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上。胡明认为:“朱熹作为一个道学家,他的诗却绝少道学气,更无头巾气、酸馅气。”71郭齐认为:“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72]许总对朱熹的创作实践做了分析,认为:朱熹的创作实践“即使是为了说明治学之理,亦全借优美的自然意象表达出来。正因这类‘不腐之作’,朱熹诗被后人称为‘道学中之最活泼者’”[73]。莫砺锋亦认为:“朱熹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丰富生活情趣的诗人,这种独特的素质使他成功地消除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并进而使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74]李育富研究了朱熹易学思想与其诗歌关系的互动,说:“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75]吴长庚则“从朱熹解易解诗之思维程序、方法、原则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朱熹的解诗思维中,他致力于诗歌比兴形象的发掘,寻求诗歌感发性情的活的功能,力求通过正确的诗解,建立一套开放性的解诗思维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易解思维中之积极成分的”。[76]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朱熹诗中的理学思想。美籍学者陈荣捷在《论朱子<观书有感>诗》一文中解释了诗中词语的理学含义。[77韩国学者李秀雄认为:“朱熹作诗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诗本身的艺术形象。他使诗中的理和趣互相和谐而达到交融的境界。”[78]日本学者申美子在《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朱子数量庞大的诗作,正是研究其一生思想形成、转变、发展极其丰富而真确的材料”,并从朱熹的诗作出发,“探讨其一生学问思想的发展轨迹”。[79]石明庆也认为,朱熹的诗歌“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80]。在朱杰人看来,“朱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抑或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对宋代的诗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公正的、充分的估价”[81]。胡迎建亦云:“了解其理学与诗歌的关系,有利于理解其诗。”[82]这同样也能进一步了解朱熹的理学思想。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章创作关系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饶宗颐对朱熹的文章做了研究,认为“朱子说理之文,逻辑性特强,又覃思者久,增、减不得,极得洗伐工夫”[83]。莫砺锋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他(朱熹)的散文写得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他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理解理学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窗口”[84。而闵泽平则深入地探讨了朱熹理学与其文章创作的关系,认为“朱熹行文的从容、平和,首先来自于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对义理的体认与把握,来自他道学气象的自然流露”[85。方笑一将朱熹的经学与文章之学相结合,认为:“与北宋儒者不同,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86另外,王仕强认为:朱熹“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87]具有典范意义。黄拔荆、周旻则“分析了朱词与其文学观、理学观的关系”[88]。许总则对朱熹理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说:“朱熹将‘义理’与‘诗文’加以遘合,表明了对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89]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明了理学对朱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以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的朱熹的文学作品。另外,通过分析研究朱熹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究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理学与文学是怎样融合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这也是朱熹文学作品对于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特殊意义。
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展望
通过以上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是开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学与《诗经》学、文道观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但研究成果多为简要的概括式论述,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港台及海外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虽然百年来学术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以至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比较而言,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进行,尚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做出一个融会贯通、整体综合性的系统研究。由于朱熹思想本身就是由文、史、哲,儒、佛、道等相互贯通而构成,朱熹理学与文学是统一于朱熹思想的一个整体。因此,研究朱熹理学不及文学、研究朱熹文学不及理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一些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某一方面的文学做过个案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作为整体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故未能揭示出朱熹理学与文学之总体特征,因此也不能进一步说明朱熹理学与文学之关系。所以目前的研究情况与朱熹既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尽管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目前的研究,确实是朱子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需要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高。在这个新的视域下,去挖掘朱熹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实质及所体现的朱子学的特点,而不是以往大多就事论事地分论朱熹的理学和文学,从而澄清和阐明朱熹理学思想中的文学性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回答其理学怎么通过其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而其理学思想里又具有哪些其他理学家不曾有的文学性等问题?从而客观揭示朱熹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及情理结合的特征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既对深入研究朱熹理学有利,也对深入研究朱熹文学有利,更对全面、综合研究朱子学有利。因此,站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朱熹思想及其价值、地位和影响,对于学术界完整理解朱熹的整个思想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我们以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为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进而展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开展:
(一)朱熹思想是在致广大、尽精微,涵盖、吸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打破界限,以融会贯通的视角去研究朱熹思想。这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学科学术研究之间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时代要求。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将朱熹的理学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仅以此促进朱子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而且拓宽了研究领域,这对朱子学的研究很有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应将具体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由于朱熹文学是由《诗经》学、楚辞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等多方面构成,我们应以这些具体的研究为基础,运用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散到联系、从局部到整体的观点和思路,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展开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并加以概括提炼,从而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系统的认识,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文化史上伦理与自然之争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尚伦理、重教化与崇自然、重情感两种文化价值观之争,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对其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其理学思想中的尚伦理、重教化与文学思想中崇自然、重情感是怎么统一于朱熹思想中的,它们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的融合又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研究的展开将为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创新的视角,同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儒学与文学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及所体现的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亦是朱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所要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某一学科的创新。某一理论学科的成就,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先导。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应采用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融合互动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上,应采取点、面、线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置于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以朱熹理学与文学为点,以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和盛行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为面,以整个中国经学史、文学史、理学史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结合,在相互联系中,做纵横比较,分析探讨,深稽博考,融会贯通,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在中国经学史与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和作用。
(四)在研究工作中,应将理论分析与训诂相结合。既要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把研究建立在考证、训诂、细读深研文本,弄清掌握朱熹经学、文学著作本义的基础上,又要避免单纯的训诂考证,而忽视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及其思想性的深入、深刻表达。
以上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仅是我们的一点意见。希望通过以上的评述和论析,在以往研究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拓展,站在朱子学促进、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时代高度,以创新的方法、理论和新视野、新材料的挖掘运用,为朱子学的研究,在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影响、结合的视域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展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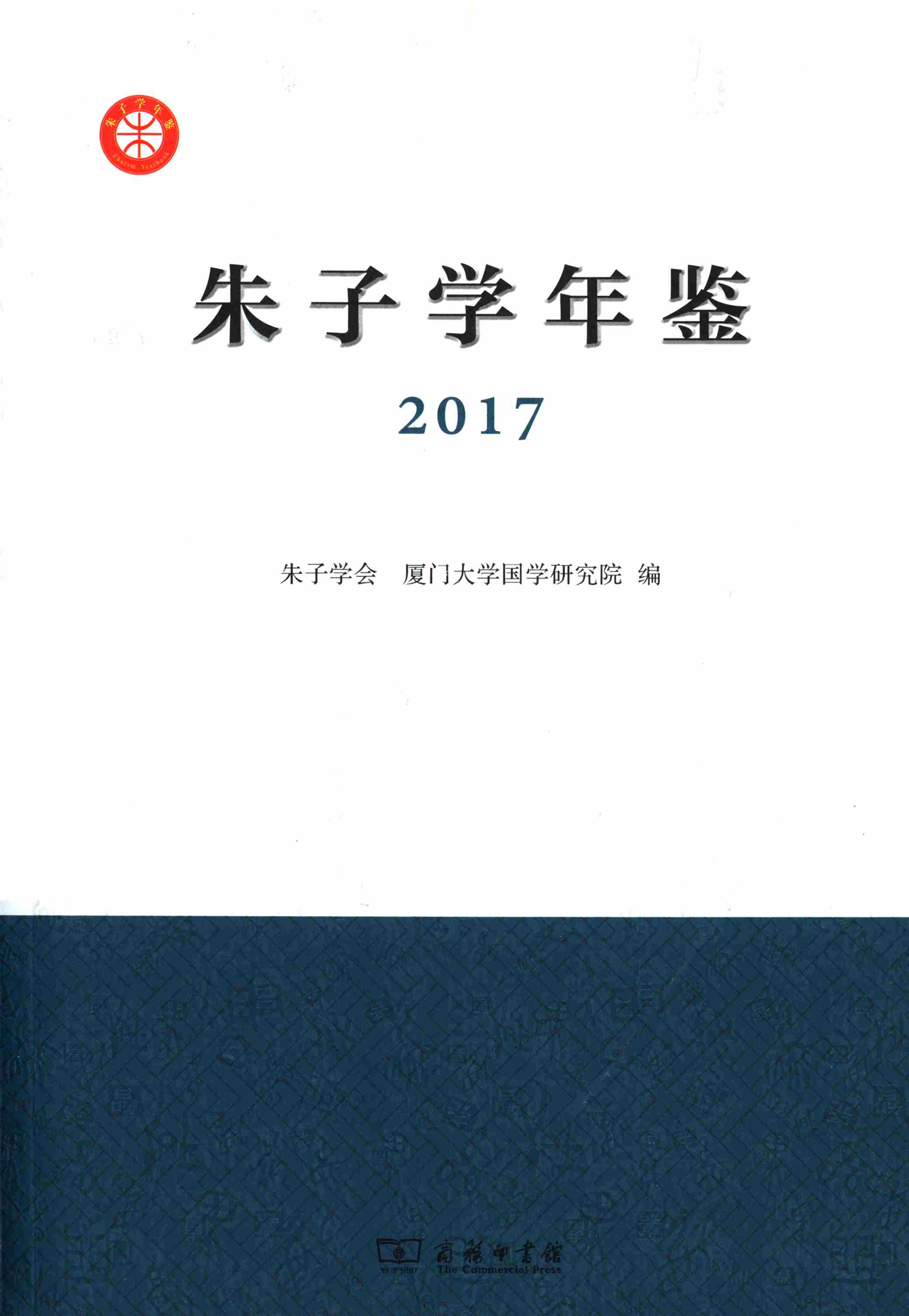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7》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仁者人也”新解》《朱子学的构建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朱熹与陈亮往来书信编年考证》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