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7》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114 |
| 颗粒名称: |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9 |
| 页码: | 163-23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包含2017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2017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2017年度日本学届朱子学研究综述、2017年度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等文章介绍。 |
| 关键词: | 朱子学 韩国 美国 |
内容
2017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
杨得煜
笔者从台湾2017年度的期刊论文当中,分别摘录数篇来进行说明[1],所摘录论文以台湾重要期刊、重要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要依据。所选择的论文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第二,韩国朱子学。第三,比较哲学。
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到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之方式作为架构。这样的架构分类可以帮助读者清楚掌握到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
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
1.陈佳铭:《朱子的“心中之理”之研究》,《中正汉学研究》29期(2017年第6期),第1~32页。
(1)问题意识
作者欲以新的观点来重新检视朱子哲学,特别是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朱子心与理之关系,在当代朱子学研究当中,牟宗三先生主张朱子言“心”是气心,心是认知地摄具理,并非是“本具”此理,故其道德实践属于“他律道德”,而不合于传统儒家的成德之教。另一位当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虽然不主张朱子属于“心即理”型态,但强调朱子系统可从“心理相合”“心理一体”,来彰显“理本在内心”之义。杨祖汉教授,则从朱子的“持敬”思想进行研究,认为朱子虽然不能肯定“心即理”,但仍然可以说“理不在心外”,进一步证成此内在于心的道德之理,也可以于心中产生动力,使此理于吾心时时产生作用,故不能说朱子不合于传统儒家成德之教。陈佳铭教授此篇论文即是基于唐君毅先生与杨祖汉教授的观点,进一步阐发朱子心与理之关系。
(2)论文架构
论文章节安排为:第一节,朱子文献中类似“本心”的概念之疏解。第二节,朱子的“心与理一”之义。第三节,格物与心中本有之理。第四节,朱子成德工夫的界限。
(3)论文摘要
首先,在现有朱子文献当中,有类似于“本心”“良知”等概念的出现,认为从这些文献的考察当中,虽然不能将朱子判定为“心即理”的型态,但是也绝不能以“心与理为二”或“他律”来规定。再者,作者进一步透过朱子批评佛教“以心求心”的工夫论,来证成朱子并非是“心即理”型态。朱子认为佛教工夫论,将主体的心另视为一客体加以观之,成了“此心之外,复有一心”的问题。佛教“明心见性”的主张,即是将“本心”当作一对象加以把握,而陷于“以心求心”的困境。而在朱子的观点中,佛教“明心见性”的主张,无异于陆、王的“逆觉体证”模式。
作者认为,朱子心与理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是“心即理”,但是可以说“心与理一”。“心与理一”具有两种意义:第一,“心本具理”。此说明了心“本具”道德之理,而此理也是“已知之理”“本有之知”。第二,理在心中发动。此说明了性理能在心气中发动。从这样的关系中来看,朱子的格致工夫意涵即是指:显发心中本有的道德之理,从自心去体认道德法则,此性理具有某种道德动力。而格物工夫也只是去体证那个“已知之理”,此“理”并非是“心外之理”。
最后,提出三个结论:第一,朱子心性论,虽然不是陆、王“心即理”的型态,但也并不能以“认知心”去理解,而是介于“心即理”与“心具理”之中间型态。第二,朱子格物型态是属于使吾心本知之理彰显、扩充出来。“格物”实为是唤醒、体证本有之理、本有之知而已。第三,此“心本具理”是一种理在气中发的意涵,此理亦可以作为道德动力之来源。
2.陈政扬:《戴君仁与唐君毅论朱子阳明格致思想异同》,《当代儒学研究》22期(2017年第6期),第39~41、43页。
(1)问题意识
戴君仁先生在《朱子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和他们整个思想的关系》一文中,表明此论文与唐君毅先生的观点可以有相互发明之处。但是,作者认为,在此之后,唐先生又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重新借梳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辨析朱子、阳明在宋明理学的思想定位。此时唐君毅先生已经有新的哲学思想发展。作者指出:第一,戴文中仅征引了唐文的结论,而未进一步勾勒出唐文汇出结论的论述轮廓。第二,戴先生作此文时,仅见唐文对朱子阳明“格致”思想的辨析,从而有必要重新考察戴君仁与唐君毅两位先生的论点。可从三个观点来审视此一问题:第一,研究方法的反思。第二,辨析道德理论之有效性。第三,反思儒学本质。
(2)论文架构
论文架构上共有四项环节:首先,先扼要地勾勒戴先生对阳明格物致知说之省察。第二,探究戴文如何辨析阳明评朱子象山说格物之失。第三,以戴先生的论点为主轴,由此对照唐先生的论点,并对比唐戴二先生论阳明格物致知说之异同。最后,在前述三点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反思戴、唐在所见略同处的儒学意义。
(3)论文摘要
作者将戴、唐二先生对于朱子、阳明解析《大学》“格物致知”思想比较出下列几点。在共通方面:第一,在解经方面,两位先生都认为朱子与阳明的诠释并不合于《大学》本意。第二,就儒学发展方面,两位先生都打破了程朱、陆王壁垒分明的对立格局。第三,就《大学》格致思想方面,两位先生皆认为朱子与阳明均是从“道德上”,而非“认知上”阐发《大学》的格致思想。
在不共方面:第一,对于阳明是否可以归属于唯心?两者见解不同。戴君仁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一切事变都是统摄于心体流行当中。唐君毅则认为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并非是朱子、阳明哲学的根本相异处。第二,对于阳明与庄子言“心”,两者见解不同。戴君仁认为庄子的“濠梁之上得知鱼乐”,可以用来解释阳明的“心外无物”。唐君毅先生则是采取儒、道二家理论本质的不可化约性的立场,认为庄子言心是“观照心”;儒家言心是“德性心”。两者在本质上有所差异,不可化约为同一。
二、韩国朱子学
李海任:《韩元震对朝鲜朱子学未发论诠释之省察》,《哲学与文化》44卷10期(2017年第10期),第163~178页。
(1)问题意识
在当前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韩元震(1682~1751)的未发理论,是对于朱熹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朱子哲学中,“未发之中”与“气禀”,此两者是不同的本质。“未发”是至善之“形上学”本体;而“气禀”是属于“形下”领域。作者对于韩元震是否继承了朱子哲学提出了质疑,欲指出韩元震在“未发之气禀”概念上,不同于朱子型态。
(2)论文架构
论文的讨论程序为:第一,可否如既有研究所主张的那样,将韩元震的“湛然虚明”规定为善的反应之根据?第二,若“湛然虚明”并非善的反应之根据,“湛然虚明”是否与“气禀”在本质上相异?第三,若“湛然虚明”与“气禀”皆非善的反应之根据,则韩元震之哲学将如何确保道德性之成立?最后,考察韩元震的“未发论”是否为对于朱熹哲学之继承与发展?
(3)论文摘要
首先考察了朱熹对于“思虑未萌”与“知觉不昧”的理解,认为朱子所讲的“未发”之“思虑未萌”与“知觉不昧”,并非意指意识的状态或流动,而是意指作为“道德性”反应之根据的“心”,此心贯通并主宰形上、形下。如此,韩元震的理论体系中,对于“未发”的定义与朱子的理解不同。“未发”更能对应“知觉作用”,而不是“道德本性”。
第二,考察“未发”问题。在韩元震的理论体系中,“气质之性”并非“未发以后”之物,而是“未发”,亦即与对象接触以前之理与气相结合的状态。
第三,“未发之心”与“气禀”的问题。韩元震并未如同朱子一样,将“未发气象”直接与“理之正明”相连接。理由在于,韩元震认为“未发之心”中,亦存在气禀。在韩元震的理论中,“心”与“气禀”在本质上是“同一”,即皆是气。
第四,圣人与凡人之“虚灵知觉”的问题。韩元震主张“圣凡心不同论”。对于韩元震而言,无论圣、凡,其“虚灵知觉”都是对外物刺激之反应的基底。差别在于:圣人之心“依理”做出反应,而凡人之心“依欲”做出反应。并且圣人之“虚灵知觉”在不同情况下,都具有能发现“法则”的洞察力。
最后,作者指出,对于韩元震而言,“未发之心”并非是道德反应之根据,而是应对外物刺激的心之“知觉作用”;人之道德性反应是建立在道德规范上(性理)。未发之本质是“知觉”,并不异于欲望;而并非如朱熹所主张的那样,是形而上的道德反应之根据。
三、比较哲学
1.陈文祥:《洞察与豁然贯通:郎尼根与朱熹论认知之心及其本性》,《哲学与文化》44卷3期(2017年第3期),第155~172页。
(1)问题意识
在当代认识论中,郎尼根提出了一套认知理论模式,让人可以从体认个别存有到存有本身。另一方面,在中国,宋明理学家之一朱熹,则发展出一套格物致知理论。这两者在认知论中具有相类的论说内涵,特别是在“洞察”与“豁然贯通”这两个主要观点上。
(2)论文架构
分四节进行讨论:第一,辨析二者理论的特征及其侧重;第二,析论郎尼根对主客认识与洞察的观点;第三,朱子讨论格物与豁然贯通的论点;最后则为讨论二者的歧异并做出结论。
(3)论文摘要
首先说明了郎尼根的“异质同形论”。从具体的认知事例中体察“洞察”的实存正是郎尼根哲学起点。所谓“洞察”观念最简单明显的定义就是“瞭悟的行为”(an act of understanding)。然而,如何定义“瞭悟的行为”?作者根据当代学者W.A.Stewart的说法:“理解的活动本身无法定义,因为理解是一种动态的活动。”郎尼根企图推论,透过洞察能力的中介,我们的认识与外在事物的关系是确实的。也就是说:第一,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进行认知活动。第二,我们也肯定了外在物的存在。如此使得认知上的怀疑论是站不住脚的。关键在于:我的认识能力与外在的被认识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相应性”,郎尼根称为“异质同形”(isomorphism)。作者指出,“异质同形”的理论与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具有相互参照的可能性。
第二,朱子言“类推”概念似乎可以和郎尼根所言之“重点不在于认识一切,而在认知者本身的体认”相呼应。从当代思绪理解朱子的认识论,则和郎尼根的“洞察论”几无分别。但是,两者并非没有存在歧异性,朱子与郎尼根的歧异在于“知识本源与根本方法”上。朱子采取的是本体论式之“内在超越”的路径;而郎尼根则是基于传统基督宗教哲学之“外在超越”的路径。
第三,郎尼根“洞察论”,其结论是洞察到唯一的创造者正是人类洞察的顶点;而朱子的“豁然贯通论”,则企图找到万物根本的理,并在伦理生活中体现此理的实存。
2.廖育正:《朱子心性论可以响应道德责任归属吗?》,《台湾大学哲学论评》53期(2017年第3期),第109~143页。
(1)问题意识
当代哲学讨论道德责任归属时,一种常被接受的观点是:“某人对某行为具有道德责任,且为某人在自由意志下,促使了某行为的发生。”若是人无从避免去执行一件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则人不应该被归属道德责任。所以,朱子心性论是否可以响应道德归属的问题?
(2)论文架构
分为五个重点章节:第一到第四节:当代学者所采取的观点。第五节:作者提出学界观点分歧理由以及方法的反思。
(3)论文摘要
如果要在朱子理气二分的义理中,讨论道德责任归属之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聚焦在朱子心性论上的诠释,才可以厘清朱子是否可以响应道德责任归属之问题。再者,对于朱子心性论观点,作者考察了当代学界的研究成果,分类成四种型态,即三种进路与一种批评。第一种进路:心属于气,无以归属道德责任。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第二种进路:心属气,可以归属道德责任。以傅武光教授为代表。第三种进路:心不能说属气,道德责任之归属无理论困难。以陈来教授为代表。最后,一种批评:“道德责任”之相关探讨不完全适用于朱子义理。以祝平次教授为代表。
“朱子是否可以响应道德责任归属?”之问题,其实是“兼容论”与“不相容论”之争的中国式案例。若“心属于气,且可以归属于道德责任”,则属于“兼容论”。反之,若“心属于气,不能归属道德责任”,则合于“不兼容论”者的思维模式。朱子的思想重心不在于保障一个先验的自由意志。而朱子深刻地洞察到“心”作为连接人与理的枢纽,知觉形上至善的天理,同时也具有形下的气禀。作者认为朱子并没有采取过康德式的预设自由意志之进路。对于朱子而言,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应该诘难的问题。要如何理解,作为朱子义理枢纽的“心”?除了从存有进路的探究,仍需并陈以工夫体验——以本体工夫论兼及体验论的视野,去照应涵养省察、格物致知、持敬、克己、致中和等思想概念丛,或许才更能厘清朱子哲学的眉目。
3.苏费翔:《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郑玄与朱熹对“慎独”的解说及西方学者的诠释》,《师大学报》62卷2期(2017年第9期),第111~125页。
(1)问题意识
“慎独”概念在传统中国思想中非常普遍,中国历代学者在这个概念上都下了诸多工夫来解释。慎独的概念同样被20世纪中外学者所重视,而出现诸多的西方翻译。翻译文本在跨文化哲学的脉络中,会对原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论文架构
论文先介绍先秦及汉代的主要相关经典。第二,从语法的角度谈论君子慎独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第三,分析郑玄和朱熹对于慎独的理解。第四,讨论东西学者欧语著作的基本立场。
(3)论文摘要
《中庸》“慎独”思想在当代学者的诠释下,其哲学含意有两个层面:一方面言人人必谨慎小心,属于修身工夫(此为学者比较重视的一点);另一方面又谈论所“显见”的“隐微”之物,并与“道”相连“所不睹、不闻”之事,涉及“知识论”领域。
“慎独”有两种角度。在《中庸》中的第一段(作者称之为A):“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段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其所不睹、不闻”指“君子被他人所不睹不闻”(作者称之为A1);其二,“其所不睹、不闻”有可能指“君子自己不睹不闻”的事。(作者称之为A2)
在《中庸》中的第二段(作者称之为B):“君子慎其独”。此段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可指“君子独居”,即“他人看不到君子”的场合(作者称之为B1)。其二,“独”又可指“君子独知”,即“只有被君子所感到”之事(作者称之为B2)。
从思想意义的角度来看:第一,【A1】与【B1】两段和“不愧屋漏”的意思很相似。第二,【A2】言“君子所不知”之事,代表最奥妙的一层面;不但隐含着任何人不睹、不闻的地方,而又可以引申无法用逻辑思想的方法来推断之事。此是谨慎恐惧到最高极限。
在郑玄与朱熹注疏方面,在郑玄《十三经注疏》中,【A】段与【B】段,都是采取“不愧屋漏”的概念,即【A1】与【B1】的解释。而在朱熹《中庸或问》中,于【A】段中,很明显的是用采取【A2】的立场。但是在【B】段中,朱熹同时采用了【B1】与【B2】的解释。
在西方学术界中,陈荣捷与杜维明的英译,两人同样都采取了【A2】与【B1】的解释。作者指出,卫方济的解释很类似朱熹,理由在于:“耶稣会传教士在解读《中庸》经文时与中国官方的学者合作,故选用以朱熹为主的解说。”当代德国汉学家鲍吾冈(Wolfgang Bauer,1930~1997),在《中庸》【A】段中,采取了【A1】的解释;在【B】段中,则采取了【B1】的解释。作者引鲍吾冈的观点,认为在【A】段中,【A1】是中国早期思想家的见解,而后来心学派将此段误释为【A2】。
当代的英译本中,对于【A】段与【B】段的解释则都采取了理雅各布的解释,即【A1】与【B1】的解释。理雅各布塑造了一个说法,影响了后来的翻译者。相较于中文,印欧语系的语言比较明确地表达动词的主动式与被动式,因而这些西方译著往往会缩小经书原文广泛的含义。作者认为翻译在跨文化哲学的脉络中会约束原文的含义。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
2017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
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韩﹞姜真硕
2017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朱子学研究、退溪学及韩国儒学研究、茶山学研究、韩国儒学的其他论辩以及东亚儒学研究等五个领域。
一、在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方面
学者们提出朱子的忠恕论、心理治疗、太极解义论、主敬论、修养论、仁说以及朱子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等主题研究。主要的论文有《朱子的欲望观及其现代意义》(Jeong Sang-bong,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文化研究》67卷,2017);《朱子道德论中的敬的地位和意义及其来源的研究》(Hwang Gab-yeon,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40卷,2017);《朱子<太极解义>一考:以其世界观为主》(Sho Hyon-seong,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39卷,2017);《关于张栻“仁”的小考》(Lee Yun-jeong,韩国哲学史研究会,《韩国哲学论集》55卷,2017);《朱子哲学的忠恕概念分析及其伦理学的含义》(Kim Hye-su,韩国中国学会,《中国学报》80卷,2017);《哲学治疗与朱熹的修养论:以心概念和涵养为主》(Ahn Jae-ho,中央大学中央哲学研究所,《哲学探求》47卷,2017);《朱熹<武夷櫂歌>与朝鲜道学者的反应》(Kim Tae-wan,崇实大学韩国文学科艺术研究所,《韩国文学与艺术》24卷,2017);《关于<周易元亨利贞的解释的比较研究:王弼、程颐、朱熹、丁若镛》(Seo Gunsik,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精神文化研究》40卷,2017);《絮矩之道与公正的主体之条件:以朱子与茶山为主》(Hong Seong-min,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41卷,2017);《朱子忠恕论的多层解释的探讨》(Kang Jin-seok,朝鲜大学人文学研究所,《人文学研究》53卷,2017)等。
1.金惠洙:《朱子哲学的忠恕概念分析及其伦理学的含义》
金教授说明“忠恕”是一个道德实践的伦理原则,是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两种原则。在中国方面,冯友兰和劳思光先生已经详细探讨过这些内容。他们主张“忠”为积极意义的伦理原则,恕为消极意义的伦理原则。就韩国学者的研究而言,他们一方面主张儒家的忠恕大体上不异于西方基督教的“你们希望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等黄金律思想,但另一方面把儒学的“恕”看作否定意义的黄金律,而且从道德义务论的角度去回应康德批判黄金律的内容。金教授介绍在朱子忠恕论中,“忠”为被作为道德本体的天道的实现,“恕”为实现公正对待的伦理原则的作用即人道。因此万事万物的“恕”是由“忠”所贯通的。金教授认为朱熹的“忠”具有义务论的伦理意义,就是说“忠”表示应当实践的道德法则,是把“理”作为“尽己”的义务来实践的。从此进一步说“忠”就是尽己之道德原理的道德意志,不仅可创造出许多的道德规则,而且通过“恕”可展开具体的实践方向。“恕”为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伦理。这是朱子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解释。
金教授又认为朱熹把“恕”的禁止给予他者损害的道德行为作为标准,这与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说的“禁止损害的原则(no harm principle)”大同小异。这种“禁止损害(no harm)”行为就是为走进最低要求的道德社会所需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也是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当今韩国社会需要的一个原则。朱子除了“推己及人”以外,还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表示人们如果要做自己的道德实践,则要把遵循内在于自我的道德法则的道德义务,积极实践于他者身上。从忠恕的角度看,“仁”是指自律的道德义务,就是主动为他人做善行及奉献的义务。这种积极意义的义务就超越应当或应该遵守的道德义务的范围,成为博施于群众之爱的道德原理。这可与道德义务的“忠”相通,也可与“推己及人”之“恕”的具体运用相应。朱子相信如果每人实践“推己及人”和“以己及人”等伦理原则,则可以实现成熟的伦理国家。
2.洪性敏:《絜矩之道与公正的主体之条件:以朱子与茶山为主》
该论文是关于朱子与茶山絜矩之道的比较研究。洪教授掌握了朝鲜时代韩国儒者对絜矩之道论辩的大量资料,因此注意到了絜矩之道具有的几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政治家不具有公正的准则即“矩”,那么就在“絜”即观察百姓的生活条件方面会产生差错,也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此絜矩之道正是政治家对待百姓时所需要的公正的态度。朱熹主张,进行“絜矩”之前,先需要道德主体的修养,要确立既普遍妥当又公正的道德主体。此修养的方法有致知、诚意正心等。格物致知是用来要把握他者之心,也是认知主体与他者间具有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由此可确认我(道德主体)的心正如他们的心。诚意正心则是指道德主体省察私欲和自我中心倾向,而后可得无私之心。洪教授认为朱子絜矩之道和恕不仅表示两人或三人在日常关系中单纯地交换立场而思考的道理,而是表示一个主体先把握公正性和道德性,然后依此来公正地对待他者的原理。一个道德主体要先确立道德性,才能公正地对待及忖度他者。由此可看,在朱子的道德实践思想中,絜矩之道及恕本身不具有一个独立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是从道德主体之树立后才能发生的一种结果。在朱熹看来,自我与他者互相交换立场或是同等对待等的逻辑概念会带来两者本身具有的恶也可被容许的一种诡辩。恶人宽恕另一恶人,互相承认对方的错是在同质化的逻辑上可被接受的。如果因为有恕的伦理会发生主体与他者互相容忍的恶,恕就不能成为一生可遵循的伦理准则。
相对的,洪教授认为茶山丁若镛的恕是指对待他者时尽己的忠实。换言之,如果没有人跟人之间的交际,就根本不存在可尽忠实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茶山说恕是根本,忠是其实践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完备一贯之道。茶山认为,《大学》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原本是语序导致的,因此我们应当念出原来的含义即“求诸人而后有诸己,非诸人而后无诸己”。这里的恕不是主体道德性的扩张,而是自我修养的方法,也是工夫的开始。我们通过恕的态度可反省自己也需要改正修养。就是说把对他者的要求找回于自己身上,把它作为自我修养的课题,这才是“恕”的修养方法。父子关系、上下关系不外如此。互相交换立场,以他者的视角反省自己,消除私心,然后一个主体才能树立公正的态度,也公正地对待他者。洪教授认为,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对他者的要求和从他者所忖度而来的情感是本人自己要实行的道德义务,在与他者交际中反省自己,要确认自己的伦理道德,就是树立公正的自我即“矩”的具体方法。此种方法是在现存的人际关系网中才能施行的,与朱子的伦理方式相差很远。
3.姜真硕:《朱子忠恕论的多层解释的探讨》
该文首先介绍孔子忠恕论与世界宗教的黄金律思想的比较。不管是犹太教、伊斯兰教或是印度教都有着与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类似的伦理思想。到了朱子,孔子的一贯之道变成忠恕体用的形而上学,即“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本体之忠根据于天道的原理,而作用之恕是本体之于现实世界的分化过程。该文介绍以往不少的韩国学者从道德义务或是道德责任的视角探讨过朱子的忠恕思想,这主要是针对康德的黄金律批判而回应的。但笔者对这些看法提出一些质疑。就是说朱子哲学不仅讲到圣人之道或是如何成为圣人的圣学工夫,并且很重视学人及凡人之道即困而知之、学而知之等修养工夫。朱熹的忠恕论也不例外,是说朱熹说的“恕”的确是包含着多层解释的话语。如果从道德义务的角度论到忠恕思想,就会局限于圣人之忠恕论题,然而在学人及凡人的忠恕,则却还需要许多的修养工夫的过程如穷理、正心等。因此拙文认为,我们要把焦点从忠恕有否道德义务的根据或是道德标准是否准确的论点,移动到孔子本来要说的是什么或是朱子原来要说明的要旨在何等主题上。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通过穷理和正心的工夫要学习及认知道德标准,由此要进行调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知和调整的过程不是被激发于道德主体自律及主动的实践一面,而是产生于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标准与忖度及反求自己不愿与不欲的侧面。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个方面。
学人的道德标准不像圣人那样生而知之的,他们不管在认识道德标准或是实践伦理原则上,都需要不断认知它的修养过程。凡人在以道德原理来判断好恶、是非的能力上都有困而知之之处。格物穷理就是对这些人最要紧的修养工夫。朱子讲到絜矩之道时,特别强调此格物穷理的工夫。道德标准不是先验地赋予我们,而是通过穷理和正心工夫后才能得到的。因此我们讲道德义务前,应该先弄清自我的道德标准,然后可把它努力做实践。凡人的“反求诸身”不仅表示一种调整自我道德标准的行为,同时也是与他者共同进行道德关系上的协调的过程。另一方面,朱子从自然与人为的角度讲过仁与恕的区别。自然的行为与人为的努力的区分反映着自律和主动地实践与需要修养和调整的实践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仁与恕的区分不是说明积极与消极或是肯定说法与否定说法的差异,而是要说明不同层次的工夫及概念。这里说的忠恕是学人和凡人层次的行为者不断寻求及探索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一个过程,也是认知自己的道德标准后把它适用于他人身上而寻找相互协调的过程,又是在此过程中把自己的道德原则强恕而行的实践行为。拙文又介绍朱子说的“三摺说”。朱熹把絜矩之道看作一种三摺之册,就是说絜矩之道不是一对一的个人伦理,而是三人以上的共同体伦理。王庆杰(Wang Qingjie)等学者把它称为共同体化。朱熹说过絜矩是在人际网络上要确认自己的本分和范围,各自重新调整自己的中心后,得出既协调又中节的共同体伦理的过程。互相共同体化的伦理倾向拒绝先验地被赋予个体的一种绝对律令或是道德义务。追求共同体化的儒家伦理不是要绝对化而是要实例化,也不是要命令化而是要协议化,又不是要规律化而是要持续教化。
上述的三篇论文,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朱子忠恕与絜矩之道,反映着当今韩国学者对朱子的伦理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4.黄甲渊:《朱子道德论中的敬的地位和意义及其来源的研究》
黄教授介绍以往当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等都主张朱子的敬思想是一个不完整的后天的他律工夫。但黄教授本人对这些看法提出一些疑问,由此就梳理了朱熹敬思想的各种内涵。该论文说明在朱子哲学里敬与虚静的关系不是说以敬为主要工夫而以虚静为附属工夫,而是虚静是个敬工夫的附属效果而已。因此在敬工夫中虚静不是个排斥的对象,也不是可代替敬的另一工夫。在朱子道德论中,敬是个能够恢复心之湛然虚明作用的工夫,这不是一种静态的工夫,倒是一种使得心之思虑作用从而完善地发现的动态工夫。黄教授介绍,朱熹的敬工夫如果一直强调整齐严肃等外向工夫就有陷入形式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必须与收敛、常惺惺、主一等内向工夫并行。无妄思是属于收敛、常惺惺、主一等工夫,无妄动是整齐严肃等外向工夫。朱子通过敬工夫完成了内外兼修的工夫。
黄教授认为,朱子说的主一和常惺惺工夫都照理作为自己的内涵。这是儒家和佛教的差异。虽然在朱子心性论中,心与理在概念和本体论上是显示二元形式,但心对理有无条件的尊敬和喜悦,理亦是以自身的法则性和至善性不断引导心。朱子说的敬是在心与理的合一状态中发挥其作用。黄教授认为敬工夫不是从心之外在到来的工夫,而是心之自觉本身。朱子的道德论不像牟宗三先生说的他律工夫,而是属于自律道德论系统的工夫论。心统性情也是由敬工夫所决定的。敬是贯通于内外、有事无事、动静的工夫,是贯串于道德的全范围、心活动的全领域的全面工夫。那么,牟宗三先生特别低估朱子敬工夫的那些误解何来?第一原因可能是朱子特别强调整齐严肃等外向工夫。第二是牟先生把朱子哲学中的性理与心的关系过度地看成认知上的摄具,因而排除了心之对性理的自发、自愿的喜悦和尊敬的内容。
笔者认为黄教授以细密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朱熹敬工夫具有的多层含义,尤其是从客观的态度重新论证了当代新儒家对朱子学的看法。
二、在退溪学与韩国儒学方面
韩国学者研究《心经》的解释、《大学讲义》的比较、哲学的比喻和象征、杨村权近的思想、霞谷的《中庸》解释、退溪的敬思想及活人心方研究以及四端七情论辩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朝鲜儒者对心修养的省察——国译<心经>注解总览》(Han Geong-gil,历史实学会,《历史实学》62卷,2017);《16世纪后期朝鲜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学论争——以<大学讲语>的经学论争为主》,(Lee Hyung-sung,韩国思想文化学会,《韩国思想与文化》88卷,2017);《哲学的比喻和象征——17世纪朝鲜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与统摄的世界观研究》(Kim Seung-young,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39卷,2017);《霞谷以朱王二元结构解释<中庸>》(Hwang Yin-ok,凡韩者学会,《凡韩哲学》86卷,2017);《时代<明儒学案>的读解情况及其性格》(Kang Gyong-hyeon,韩国阳明学会,《阳明学》46卷,2017);《初期退溪学派门人对<心经附注>的理解和退溪学的心学倾向》(Lee Sang-ho,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34卷,2017);《从退溪与杨明的修养论的比较研究考察朝鲜时代阳明学未扩散的原因》(Kang Bo-seng,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文化研究》68卷,2017);《退溪李滉的<活人心方>与诗形象化》(Xia chung-won,韩国文化融合学会,《文化与融合》39卷,2017)等。
1.金昇泳:《哲学的比喻和象征——17世纪朝鲜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与统摄的世界观研究》(《儒学研究》39卷,2017)
金教授收集大量的文献,从而介绍了17世纪韩国儒者所使用的许多比喻和象征的内容。他涉及的文献内容十分广泛,因此他的论文值得参考及引用。他介绍退溪学派的儒者活斋李榘(1613~1654)。李榘活动时期正好是李栗谷的学说逐渐扩散的时期,此时他用几个比喻来辩护退溪哲学的宗旨。他说“愚谓理犹柂也,气犹船也,心犹人也。非船则柂无所掛撘,非柂则船不能运行。主之者乃人。有时柂动而船随以行,有时船发而柂乘以运。人或任船而行,不无胥溺之患,必用柂以运自有利涉之道也。”(《活斋集》卷三)由此李榘强化了退溪哲学的理气互发说。沙溪金长生(1548~1631)用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格物说。他提出格物的比喻,支持李栗谷的格物论而批判郑经世(1563~1632)的“请客而客来”(这里请客指格物,客来指物格)的看法。金长生说“譬如暗室中,册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而缘黑暗不能见物,不可谓之册衣箱在其处也。及人灯以照之,则方见册衣箱各在其处分明,然后乃可谓之册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极处,非待人格之而后始到极处也。只是人之知黑暗未能见理,则岂可谓之理到极处耶。理非自解到极处,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到未到也。”(《沙溪遗稿》卷四)
愚潭丁时翰(1625~1702)用月光的比喻说明理与物的关系。他说“天上之月光,虽不以物之清浊虚实,照有不遍,而浊实之中既不见月之光影,则不可谓浊实之中月光之本体存焉。若以隐于无形,谓浊实之中月光之本体存焉,则是求理于悬空,无用之地,而其所谓本体之明于何见得乎。”(《愚潭集》卷四)尤菴宋时烈(1607~1689)用器与水的比喻来说明心性情的关系。他说“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中泻出者也。只言虚灵而不言性情,则是无水之空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虚灵,则是水无盛贮之处也。是三者缺一,则终成义理不得,岂得谓之明德乎。盖或者之意以所谓虚灵不昧者为释明德之意,故有此说。而不知所谓明德者是心性情之总名也。”(《宋子大全》卷一〇四)明斋尹拯(1629~1714)用行路的比喻说明“格物”与“物格”的差异。他说“今以行路言之,行路格物也,路尽物格也。欲至某处者致知也,既至某处者知至也。今曰人欲至某处则当行路,路既尽则已至某处矣。如此看,岂非晓然耶。然则,欲至某处既至某处者,主人而言也。”(《明斋遗稿》补遗)
笔者认为金昇泳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朝鲜时期韩国儒者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和象征比喻方面的许多资料。如上介绍的“理犹柂也,气犹船也”“请客而客来”“人灯以照之”“天上之月光”“器与水的比喻”“行路的比喻”等话语不仅丰富了朝鲜时期韩儒的思维方式,也显示了他们对朱子学的理解内容。
2.姜卿显:《朝鲜时代<明儒学案>的读解情况及其性格》(《阳明学》46卷,2017)
该论文提供朝鲜时代的韩儒如何运动及理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文献的事实。照姜教授的研究,当时读解《明儒学案》的韩国文献有《青庄馆全书》(19世纪初)、《研经斋全集》(19世纪中期)、《五洲衍文长笺散稿》(19世纪中期)等。这些文献都是属于明代人物及思想的一种资料集。因此可知,当时这些文献的作者都把《明儒学案》看作一种可参考的资料文献,他们把《明儒学案》运用为可参考明代人物的行迹和言说的一种传记类的文献。他们不太重视《明儒学案》由黄宗羲的视角所编撰的事实,只是用来收集有关明代人物的史料。
当时韩儒李圭景正视了在《明儒学案》中列举的人物包括朱子学和阳明学等各种学派。他不因其书倾斜于阳明学而排斥它,而是从圣门的宏观角度容纳它。姜教授认为李圭景一类的看法反映着当时学者把《明儒学案》看成明代各种学派的思潮史料,以此可参考朱子学和阳明学等思想。相对的,当时李裕元一类的学者从朱子学的角度批判地看待《明儒学案》。他说“盖其书两学俱载,其言论义理,如镜照而烛行,自可发明。余钞作一书,编于笔记之末,俾自解其正邪之别云。”(《林下笔记》卷7)这两种类型的学者们对阳明学都有一定的批判的态度,但是他们总算不完全排斥明代盛行的两种学潮的史料事实。但是到了第三类型的学者们,对阳明学的批判相当猛烈。姜教授介绍属于第三类型的韩儒有吴熙常(1763~1833)、洪直弼(1776~1852)、田愚(1841~1922)等人物。特别是吴熙常说明儒除了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以外没有可参考的,认为这三人以外,大部分的学者脱离朱子学各自树立门派,结果都流于禅学。韩国的阳明学派运用《明儒学案》史料的事实,在朝鲜时代中没被考证。到了日本殖民时期,在朴殷植(1859~1925)的《王阳明先生实记》和郑寅普(1893~?)的《阳明学演论》中,可找到被引用的记录。
三、在茶山丁若镛研究方面
有《丁若镛与李震相的公七情说的比较》(Lee jong-woo,《洌上古典研究》56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游览及纪行中凸显的风流及其意义:以记文与纪行诗为主》(Kimjong-ku,韩民族语文学会,《韩民族语文学》76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风水观:批判与继承》(Lee Kong-sik,Chon Yin-ho,釜山大学韩民族文化研究所,《韩国民族文化》64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实践德论的考察》(Oh Soo-lok,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文化研究》69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侄女丁兰珠的在济州岛的流放生活与天主教》(Hong Dong-hyon,延世大学茶山实学研究院,《茶山与现代》10卷,2017)等论文。
在此,着重介绍李宗雨教授《丁若镛与李震相的公七情说的比较》一文。李教授介绍韩国儒学的“公七情”说。此公七情学说是韩儒星湖李瀷(1681~1763)在解释李退溪与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辩时所提出的。后来受到李瀷影响的茶山丁若镛(1762~1836)与寒主李震相(1818~1886)对这些学说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李瀷门人针对李瀷的公七情,各自提出公七情理发和公七情气发等不同看法。后来丁若镛受到李瀷的影响主张公七情是从天命而发的,说“凡公喜公怒公忧公惧,其发本乎天命”。但李震相认为公七情是理发的,他说“星湖晚年,亦主公喜怒理发之说”。茶山批判天命之性为理,七情之发为气等说法,也不同意朱熹的性即理等学说。韩国学者对丁若镛的说法议论纷纷,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茶山受到《天主实义》影响的原因。但有些学者主张丁若镛受到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的影响。李教授介绍当今学者李光虎教授主张茶山年轻时在《中庸讲义补》支持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但到四十岁以后在《理发气发辩》中受到退溪之理发说树立了上帝说。相对的,李震相主张七情也有理发,但不是每个七情都是理发,而是发而皆中节才有理发的。
四、在韩国儒学的其他论辩研究方面
主要论文有《济州的朝鲜儒者边景鹏的双重文化认同》(Kim Chi-wan,韩国文化融合学会,《文化与融合》39卷,2017);《南堂朴昌和对韩国疆域的论辩和认识》(Park Nam-soo,新罗史学会,《新罗史学报》41卷,2017);《西厓柳成龙的阳明学批判》(Choi Jong-ho,东亚人文学会,《东亚人文学》38卷,2017);《从儒学到汉学:20世纪60年代之后韩国儒教政治运动的衰退过程研究》(Lee Hwang-sik,东洋社会思想学会,《社会思想与文化》20卷,2017);《在近代话语中儒学者李树廷1 885年把<马可福音<翻译成韩语的意义》(Kim Shin,21世纪基督教社会文化学堂,《神学与社会》31卷,2017);《田愚的西学认识及其斥邪论:以<自西徂东辨>和<梁集诸说辨>为主》(Lee chong-lok,朝鲜时代史学会,《朝鲜时代史学报》80卷,2017)等。
金信教授的《在近代话语中儒学者李树廷1 885年把<马可福音>翻译成韩语的意义》一文较为突出。金教授介绍朝鲜后期儒学者李树廷(1842~1886)一生致力于翻译基督教《圣经》的时代意义。李树廷活动于封建朝鲜的没落与近代社会的转变的交叉时期。李树廷一方面坚持朱子学者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回心,从此开始做翻译工作。他的《圣经》翻译是到日本之后正式开始的。当时他把Bridgman与Culbertson翻译的《旧新约圣书》作为原始资料,以及在传教士Henry Loomis(1839~1920)的助力下所成的,然而李树廷始终吸收朱子学的思想资源。金教授简略地介绍韩国的《圣经》翻译史。自从1877年苏格兰传教士John Ross(1842~1915)和李应攒一起把中文《圣经》翻译成韩文《圣经》以来,1878年他们又翻译了《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以及与徐相崙(1848~1926)一起完成了《路克福音》的翻译。1879年John McIntyre和白鸿俊一起翻译了《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以及《罗马书》等。1882年,中国沈阳的文光书院首次出刊了韩文《耶稣圣教路克福音全书》和《耶稣圣教路约翰音全书》。1885年在日本,李树廷出版了《马可福音》的韩文翻译本。李树廷的翻译工作具有先设定读者对象的一个特色。他的翻译是针对当时懂汉字的知识分子而做的。因此与专用韩语来翻译的Ross的翻译不同,他采取汉韩文并用的翻译方式。这种圣经翻译叫作“悬吐圣书”。
笔者认为金教授的论文提供了朝鲜末期朱子学者受基督教影响下分化的一个脉络。这为韩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在东亚儒学研究方面
主要论文有《董仲舒哲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Hong Won-sik,东亚人文学会,《东亚人文学》39卷,2017);《梁启超的格义西方哲学研究》(HwangZhong-won,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42卷,2017);《伊藤仁斋的儒教概念中凸显的古义学体系及其理念——以<论语古义>的概念分析及宋儒批判为主》(Lee In-hwa,韩国东西者学会,《东西哲学研究》85卷,2017);《山鹿素行的<中庸>解释——以与朱子的心性论做比较为主》(Lim Ok-kyun,东洋哲学研究会,《东洋哲学研究》90卷,2017);《山鹿素行的<大学>解释——以与朱子的心性论做比较为主》(Lim Ok-kyun,东洋哲学研究会,《东洋哲学研究》89卷,2017);《近代日本的“修身”理解——以荻生徂徕与山鹿素行的思想为主》(Tokusike Kumi,An Hae-yeon,釜山大学人文学研究所,Cokito82卷,2017)等。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7年度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福谷彬廖明飞译
和2016年一样,2017年度日本学界有关朱子及其后学思想(狭义的“朱 子学”)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扩大了收录范围,介绍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的宋学 研究(广义的“朱子学”)的最新进展。本文分专著、单篇论文依次做介绍,最 后总结本年度的研究并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
ー、专著
1 .下川玲子⑴:《从朱子学中思考的权利的思想》⑵
该书从权利思想的观点出发,重新检讨朱子学在日本的意义,提出朱子学的 尊严论与西洋式权利思想具有亲和性,与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权利思想相似,探 寻如何能够活用权利概念及朱子学的思想。全书目录如下:
Ⅰ朱子学の論理と人権の論理
第1章 西洋の権利の思想
第2章 朱子学の尊厳論
第3章中江兆民における朱子とルソーの受容
第4章 近世儒教を把握する視点
Ⅱ朱子学の現代的諸問題
第1章 寛容論と権利の思想
第2章 武士道の論理と権利の思想
第3章 死刑廃止論と朱子学
第4章福祉国家論と朱子学
该书指出,日本前近代的朱子学,不单是被西洋的近代思想驱逐的旧思想, 在接受西洋的近代思想方面也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的主张,以在日本的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名著——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批 判性的前提。以下,在介绍丸山著作内容的同时,对此主张加以评价。
丸山将荻生徂彿视为日本近世思想成立的划时代的人物,认为被徂彿学否定的朱子学是前近代旧思想的典型。根据丸山,朱子学的“道”并非由人创造,而是天理的自然。与此相对,对荻生徂徕而言,“道”是圣人通过“人为”(“作为”)创造出的制度和文物。依据朱子学的观点来说,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一般想法,本来应该是与“天理的自然”一致的,不应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与此相对,荻生徂徕认为,社会的秩序是统治者通过积极“人为”(“作为”)创造出来的,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必须根据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重新创造出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社会的一般想法。丸山指出,江户时代思想的变化,与西洋从基督教神学的“自然”观念到以托马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人为”(“作为”)思想的变化过程相似。从这一相似变化中丸山探寻“近世”究为何物。如此,丸山描绘的日本近世史观就是朱子学(“自然”的思想)的解体,徂徕学(主体性的“人为”[“作为”]的思想)的勃兴的过程。
下川氏对丸山的批判,其矛头指向的是丸山以霍布斯为到达点的近世史观和对朱子学在近代日本的影响力持否定性理解的态度。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如果没有统治者的管理,民众甚至无法生存,民众必须将“自然权”的一部分委托给统治者。霍布斯肯定民众无法批判君主的绝对王权。下川氏指出,这样的相比民众个人的权利,以政府的意向为优先的观点,是与“近代”背道而驰的。
与此相对,下川氏发现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权”论是近代思想的到达点。洛克论述了为了保卫民众本来的权利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下川氏从这样的尊重人们权利的观点中找寻出“近代”,从这一观点出发思考朱子学。
下川氏着眼的是朱子学的人性论与西洋的人权思想的相似性的观点。朱子学的性善说认为,人无论贵贱,生来即平等地具有绝对善的本性。下川氏指出,“自然权”(natural rights)一语,日语也翻译作“天赋人权”。正如这一语言本身即是以朱子对《中庸》“天命之性”的解释为典据[3],它清楚地表明,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在荻生徂徕是没有的,反而是朱子学的人性观才具有与西洋式的价值观的亲和性。如上,下川氏从多种角度阐述朱子学的价值观和近代性的价值观的相似点。
二、论文
1.中嵨谅[4]:《陆学的“人心”“道心”论——追踪所谓“朱陆折衷”的渊源》[51]
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先行研究认为,以折衷朱子和陆九渊的思想为目标的“朱陆折衷论”,在陆九渊的门人弟子一派中有显著的立场。[6]与此相对,中嵨氏指出,“朱陆折衷”的立场,不仅陆九渊的门人弟子一派,陆九渊自身的思想也已经有此端倪,而且,朱陆学问的决定性的决裂,是由陆九渊的高弟杨简造成的。
中嵨谅特别讨论了围绕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出典的“人心”“道心”的解释。中嵨氏检讨围绕“人心”“道心”的朱子对陆九渊的评价,又通过考察陆九渊及其初传、再传弟子的“人心”“道心”论,阐明了朱陆及其门人弟子如何面对朱陆对立的问题。
首先,作为朱陆议论的前提,有程颐的“人心道心”论。程颐将“人心”理解为“人欲”,“道心”理解为“天理”,截然区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是理应消灭的恶之心,“道心”是理应张扬的善之心。朱子最开始赞同程颐的这一说法,后来改变了立场。[7]1
朱子考虑到如果将“道心”视为天理,“人心”看作“人欲”的话,本来应该是同一之“心”会变成有两个心,所以朱子主张认识到道理时就是“道心”,感觉到声色臭味时就是“人心”。朱子认为,“人心”“道心”称呼的不同,是同一之“心”在面对不同对象之际心起到的作用有不同,因此才有二者的区别。
又,中嶋谅分析关于陆九渊的“人心道心”论。陆九渊的“人心·道心”论的特征是强调“人心”和“道心”的一致。但是,陆九渊并非倡导“人心”具有无条件的善性,而是重视《尚书·多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之语,即使是同一之“心”,也会因其心端正与否,而有“圣”和“狂”之别。因此,朱子解释“人心惟危”,认为是表达了心能够变恶的危险性。
朱子对陆九渊的“人心道心”说给予高度评价,批判程颐的说法。此后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强调“道心”和“人心”的一致,在主张“人心”非恶上与陆九渊之说方向相同。中嶋谅指出,关于“人心”,朱子与陆九渊抱有同样的见解,虽然朱子批判陆九渊迷信心之善性,但如果正确地解读陆九渊的著作,则可知陆九渊并没有朱子所批判的那种主张。
其次,中嵨谅考察杨简(慈湖,1141~1226)的“人心道心”论。中嵨谅通过分析《慈湖遗书》所收《论论语上》《论中庸》《泛论学》的内容,指出杨简将“心”看作完美无缺的善,否定心需要外在的修养。因此,中嶋谅指出,杨简的“人心”论与陆九渊强调心的修养和学问的必要性的“本心”论完全不同,杨简曲解了陆九渊的“本心”论。
最后,中嶋谅进而考察与杨简齐名的陆门高弟袁燮(絜斋,1144~1224)和钱时(融堂)的“人心·道心”论,指出他们的思想与陆九渊相同。
通过以上的考察,中嵨谅得出以下的结论。(1)陆九渊、袁燮、钱时绝非仅强调心的善性,相反,他们倡导学问修养的必要性,而杨简的主张中不能看到这ー倾向。显然杨简的立场在陆学一派中是特异的存在。(2)关于“人心・道心”论,朱子同意陆九渊的见解。在此意义上,陆学本来并没有从正面与朱子的思想相对抗,是杨简造成了陆学与朱学对立的尖锐化。(3)过去杨简被视为陆九渊最有力的继承者。但是,根据中嶋谅的研究可知,在有“甬上四 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之称的陆门高弟中,与师之陆九渊思想立场 最为乖离的即是杨简其人。
2.林文孝⑻:《“仁と為す”抑或“仁を為す”:根据朱熹〈集注〉的〈论 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的训读》[9]
“训读”是将古代汉语的汉字按顺序排列改写翻译成日本古语的传统的解读古代汉语的方法。因此,毋庸赘言,即使关于“训读”的研究作为日本人而言有多重要,作为没有必要使用“训读”的中国人来说,则完全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本文特别要介绍该篇论文,是因为在此篇论文中考察的如何训读 的问题关系到对朱子思想的理解。
林氏的论述举出的问题是:如果根据朱子的注释,《论语•颜渊》“克己复 礼为仁” ー节应该如何训读。此条经文及朱子之注如下:
【经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朱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 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 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 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
根据林氏,日本的论文所见《论语》此条经文“克己复礼为仁”的“为仁”的训读有两种:(1)训读作“仁と為す(看作仁)”[10],(2)训读作“仁を為す(做仁)”[11]。但是,关于《集注》的“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的“为仁”,(1)(2)两种场合都训作“仁を為す”的占了大部分。也就是说,(1 ) 的立场,经文和朱注的“为仁”的训读是不同的。
如上,朱子将“克己复礼”的“克”解释为“胜”,将“己”解释为“身之私欲”,将此条经文解释为是在阐述“灭人欲、存天理”的道理。问题是“克己复礼为仁”的“为仁”的解释。如果训作“仁と為す(看作仁)”,则孔子是说“克己复礼”就是“仁”。与此相对,如果训作“仁を為す(做仁)”,则孔子是说通过“克己复礼”来“实践仁”。这并非仅仅是ー个字的解释的问题,而是关 乎“克己复礼”和“仁”的关系这ー重大的思想问题。
在朱子的注释中,“克己复礼为仁”的注有“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如前(1)(2)的立场关于经文的训读是对立的,关于朱注则都以“仁を為す” 的意义做训读,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问题是关于经文,本来与注ー样应该按照“仁を為す”的意思理解,但《语类》中确实存在说明应当按照“仁と為す”的意思理解的记录。”2]林氏考证这些说法的时期,指出相比按照“仁と為す” 的意思理解的时期,按照“仁を為す”的意思理解的是朱子晚年时的记录。[13]
通过以上的考察,林氏指出,朱子对经文和注的理解都是“仁を為す”的 意思。
最后,林氏还言及“仁を為す”和“仁と為す”的解释不是互不相容的矛 盾。“仁を為す”的实践,指的不是开拓未知的地平的行为,而是回归人的本来 状态的行为。如果保持达到实践“仁を為す”(做仁)时的视点,该行为的主体就在成为“仁”的状态,也即与“仁と為す(看作仁)”一致。也就是说,朱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时的“为仁”,有读为“仁と為す”和读为“仁を為す”两种意义。虽然朱子对此做了大致的区别,但并没有做截然的区分,两种意义有 重合的地方。也正因此,两种解释都能够成立。
3.福谷彬”句:《陈亮的“事功思想”及其孟子解释》[15]
福谷讨论的陈亮(号龙川,1143〜1195)是与朱子有过“义利•王霸”论 争的思想家。
“事功”主义的表述,是朱子批判陈亮的语言。“义利・王霸”之语典出《孟子》,一般来说,相比结果和利益,孟子是更加重视动机和道德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正如陈亮的思想被评价为“事功主义”或“功利主义”ー样,他的思想容易被认为相比动机的善恶更看重功利的大小。因此,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多认为陈亮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是对立的。但是,实际上陈亮从年少到晚年都写过尊崇《孟子》的文章,经常引据《孟子》展开自己的论述,反复申说比“利”更应该重视“义”。福谷留意到陈亮尊崇《孟子》的侧面,从陈亮是如何解释《孟子》这ー角度岀发,试图重新解明陈亮的思想。
福谷以陈亮三个时期的著述《六经发题》、朱陈论争、《勉强行道大有功》为例,指出这些时期陈亮有着ー贯的主张。此中,尤其重要的发现是,一般认 为完全水火不容而告终结的朱陈之论争,实际上陈亮接受了朱子的部分说法, 对自己主张加以修正改变。
陈亮在这场论争中,主张汉唐君主的政治中天理并非总是不存在(“无常泯”)。[⑹与此相对,朱子反驳陈亮的说法,认为天理并非总是不存在(“无常 泯”),也就意味着存在没有天理的时候(“有时而泯”)。[17]
陈亮接受朱子的批判,主张三代圣王和汉唐君主虽然“本领(根本)”相同,但因为有“工夫”的差别,因而王道的完成度有差异。[⑻也就是说,陈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汉唐不是理想的王者,他们的“工夫”不足。这是陈亮在与朱子论争之前不曾有的主张。但是,在这ー论争中,陈亮完全没有言及关于 “工夫”的具体内容。
对此加以论述的是陈亮晚年的著述《勉强行道大有功》。福谷指出,在该文中,陈亮阐述道: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抱持“喜怒哀乐爱恶”的感情,而是与万人共有该感情,就能够实现王道政治,故将之题名为“勉强行道”。又说,正因为不能做到这一点,汉武帝虽然英明,也不能成就如三代圣王般的功绩。[19]
福谷通过全文的论述,将陈亮的思想做了如下总结:陈亮认为追求包含自己在内的万人的利益为“义”,只追求一己的利益为“利”。陈亮的这一思想,与朱子形成鲜明对比。朱子认为“无所为”的动机的纯粹性为“义”,盘算追求利益是“利”,消除盘算“利”之心,才能生发出止无可止的道德心的“义”。与此相对,陈亮认为,谋求并非一己而是万人之“利”的公共性即是“义”。如此,朱子和陈亮对“义”和“치」”的理解不同,朱子对“义”“利”的理解是二律背反,而陈亮认为扩大“利”的受益者就是“义”。福谷指出,这样以利益的公共性为核心的陈亮的义利观,是以《孟子》中游说统治者施行王道政治取得 治理政绩的记载为根据的。[20]
根据以上论述,福谷在该文的结论部分指出,以追求自身利益之心为岀发点的陈亮的思想,具有鼓励追求万人利益的特色,这ー想法,挖掘出与朱子不 同的解释《孟子》的可能性。
三、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知,2017年与2016年一样,狭义的朱子学研究不多,对朱子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一起加以考察的论著较多。又,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擅长精细的经学研究和踏实的文献学研究,类似下川玲子氏《朱子学から考える権利の思想》这样旨在重探朱子学现代意义的著作,则是很稀有的尝试,今后研究者也 可以在这一方向上多加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伊东贵之编《“心身/身心”と環境の哲学:東アジアの伝 統思想を媒介に考える》和细谷惠志著《薛環と明代朱子学の研究》两书均为 2016年出版的著作。因笔者的疏忽,2016年的研究综述中未予以介绍,因此, 将编入本年度的研究目录中。敬请读者朋友谅解。
(作者单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
2017年度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在过去一年,美国有不少涉及朱子学的研究。本报告将按专著、论文、会议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排序对有关成果逐一介绍。
一、专著
刘纪璐教授(JeeLoo Liu)于2017年出版了其新著《新儒家:形而上学、精神与道德性》(Neo-Confucianism:Metaphysics,Mindand Morality)。[1]该书集中分析了数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全书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新儒家形而上学的思想,共收入四篇论文。第一章讨论了周敦颐“无极”和“太极”的概念,以及其“无极”的思想与以前“无”的思想的关系。第二章分析张载的气论,指出张氏把“气”引入其形而上学和道德学说之中。第三章主要考察二程与朱熹的形而上学。作者讨论了在他们的哲学体系当中,自然是否偶尔生成,抑或其中存在着一个法则?通过将他们的形而上世界观注释为规范的现实(normative reality),作者指出三人都将天理视为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法则,其中总体的法则主宰着个别的事物。第四章则将焦点放在王夫之如何发展气论。她认为王夫之是新儒家气论与天理的集大成者。在其理论当中,自然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是浑然为一的,两者都被气与天理所支配。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新儒家学者的道德思想及人性,以及各人的分歧。第五章首先考察了朱熹的人性论。作者指出于朱熹而言天理或太极是世间最高的法则或标准,而它们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道德准则也是以天理为依归。第六章则讨论了陆象山和王阳明的道德观。作者指出两人均有别于程朱学派,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或将人的思维看成是天理本身。第七章则分析了王夫之有关人性的论述,其中气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气是变化无常的,故人性也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且受人的感情和欲望等影响。
该书的第三部分以当代的伦理学和心理学来剖析新儒家学者关于人性与道德的思想。第八章以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为出发点分析张载的道德哲学,并认为张载主张人的道德是一步步,自发地发展而成的。第九章指出有别于张载,二程认为人的道德于不同处境之中都是相同的。而他们的教育便是要培养人们这种道德感。第十章探讨朱熹有关如何成圣的思想。她以道德认知论为视角,讨论了朱熹如何鼓励人透过对个别事物、人性的理解去掌握天理。第十章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视为一种“较高级的感知”(higher-order perception)。以道德反思论(moral reflflexivism)为基础,她认为王氏的良知说是指人具有自我管束与纠正的能力。第十二章分析了王夫之的社会伦理学。根据她的描述,王氏并不认为道德可与社会割裂。社会对人的道德成长有一定影响。
二、论文
除专书以外,2017年亦有数篇涉及朱熹的论文出版。首先,田浩教授(HoytCleveland Tillman)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学生对当代朱子婚礼的看法》(“Reflflections on Chinese Student Opinions on the Modernized Zhu ConfucianWedding”)的论文。[2]这篇论文收录在《日常生活以外:纪念何尔曼教授六十五岁大寿论文集》(UberdenAlltaghinaus:Festschriftfurthomas O.Hollmannzum 65.Geburtstag)之中。这篇论文可说是数年前他与女儿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合撰之论文的延续。[3]田浩教授在文中通过分析和比较从中国几所大学的大学生之中所得到的数据,来探讨现代学生对于经朱杰人教授改革后的朱子婚礼的看法。这些大学包括南方的杭州师范大学、北方的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作者在2010年的文章中对后三者已有详细的分析,故此文只概括其中的调查结果以做比较之用)。以下是一些在调查中值得留意的地方:
(1)性别差异对学生接受有关礼仪与否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杭师大的受访女学生较留意仪式的美感,受访男性却不太在意仪式美丽与否,更着重其对家庭的重要性。
(2)大多数受访者(不论是南方或北方)都不认为经朱杰人教授改良的朱子婚礼的美感足够使人们接受和采用。
(3)受访者认为仪式当中所朗读的古文会令人却步。
(4)尽管受访者希望有足够的自由度去安排婚礼,但他们仍希望父母(尤其是男方的家长)提供协助。这在北方尤为明显。据作者所言,多数北方大学的受访者认为婚姻非是单单两个人的事。
(5)调查显示南北两地学生观点上的一些差异。例如,南方的学生普遍不认为朱杰人改良的朱子婚礼与传统差距很大,可是北方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则认为他的版本与传统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推断这可能反映了北方大学生对 传统的喜爱,而南方学生较重视美感。不过作者也指出,调查仍未能全面反映 相关的地域差距。
尽管作者在文末强调有关调查有其局限,但他认为,朱杰人教授或其他人 在推广传统婚礼时,有关数据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Eiho Baba亦于《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发表 了《“矢口觉”在朱子哲学中作为认知与理解能力:通过“魂”和“魄”所作的 一・个考察》(“Zhijue as Appreciation and Realization in Zhu Xi: An Examination through Hun and Po")一文。"’这篇文章通过“魂”和“魄”这两个概念考察“知觉”在朱子哲学体系中的意思。作者认为,“知觉”是ー个精神物理学上的过程。它拥有一种能对不同环境和各种复杂的关系中的正确行为做出认知性的 评价的能力。作者继而指出,“知觉”并非ー种对既定事实的被动性的感知。相 反,它是ー种能参与对世界进程做出决定(participatory co-determination of the world)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通过对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训练来获得的。
又Larson Di Fiori和Henry Rosemont合撰之《论〈论语〉中的仁》 ("Seeking Ren in the Analects")亦引用了朱熹有关“仁”的解释。仁的意思历来均为研究《论语》者关注的课题之一。此文认为在阅读《论语》时,人们不应将孔子视为ー个意图建筑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而应将之视为一位希望教导 学生的老师。因此,我们应以学生如何与孔子讨论仁作为切入点来理解仁这个 概念。文章中段提到朱熹的注释也注意到孔子在论仁这个概念时会因情况而做出改变,而孔门学生在其中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仁并非ー个抽 象而绝对的标准。相反,它是个人与他人相处时的行为准则。
三、会议论文
在2017年10月份,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estern Branch)年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其中有两篇报告讨论了朱熹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书信来往。第一篇是《朱熹与陈亮书信中的抱膝诗》(ル函 on ''Embracing Knees ‘‘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Zhu Xi and Chen Liang),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课程的博士生黎江南(Li Jiangnan )。这篇文章议论了朱熹和陈亮在利用书信往来时,陈亮希望朱熹为他写一首抱膝诗的事件。作者认为这起事件反映了两人对诸葛亮态度的转变,和指出朱熹试图与陈亮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考虑到朱熹本身的知名度以及信件在当时流传的程度,作者认为朱熹在这件事情中使陈亮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此,对这起事件的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二人辩论的内容,以及将他们思想上的转变与社会因素和其语言使用的方法结合起来一同思考。
另一篇报告题为《送信的方式及其对文人交流的影响:以朱熹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为例》(“The Way of Delivering Letters and Its Impact on Communication:ACase Study of the Letters between Zhu Xi and Others”),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任仁仁(Ren Renren)。通过分析约2900封朱熹与其友人所写的信件,他在报告中指出他们主要利用三种途径去送信:通过官方的邮寄系统(附递);通过专人送信;最后为通过学生或朋友送信。作者指出上述各种送信方式对于文人沟通而言有一定的影响。
四、学位论文
2017年美国大学共有两篇博士论文与朱子学研究有关。第一篇是由Courtney R.Fu博士所撰之《文人与“地方”的建构:帝制晚期的泉州文人社团》(“Literat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Local”:The Quanzhou Community ofLea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6]这篇论文是对泉州所做的一个社会文化史研究。以该地区“清源学派”,即那些学习程朱思想的学者群为切入点,作者考察了该地区的文人精英与当地的关系。这篇论文指出“清源学派”的文人具有双重身份:乡绅与乡官。作为乡官,这些文人试图通过对将该地区的文化水平进行评估来把他们与帝国政府连接起来。当地朱熹的学术谱系以及后来的程朱学者因而成为了“清源学派”推动泉州成为当时学术中心的文化符号。而作为乡绅,“清源学派”的文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自认为得程朱学术之正统而不曾做出任何改变。事实上,为了保障其福祉与生计,他们会违反政府的禁令而进行海上贸易,并积极推广重商的价值观。可以说,这篇论文是研究朱熹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
另外一篇有关朱熹的博士论文为张蕴爽博士(Zhang Yunshuang)的《透视的私隐:宋代的书斋与空间》(“Porous Privacy:The Literati Studio and Spatialityin Song China”)。[7]她的论文考察了宋代书斋的空间性问题。她指出书斋一方面提供了私人空间予文人进行文学活动,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外开放予个别文人,让他们得以在内交流以及成为他们的身份象征。尽管朱熹并非该文主要讨论的对象,它亦介绍了朱熹对于书斋的一些论述。例如在第二章中,她描述了朱熹是如何讨论书斋与读书(道德修养)的关系,以及书斋的环境如何为他带来“至乐”的境界。同时,作者亦引用了不少朱熹所撰之文章、诗词和书信,如《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答许顺之》等。故此,即使这篇论文涉及朱熹的地方不多,但却让我们从另ー个侧面了解朱熹对于外在环境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关 系的看法,以及探讨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关系。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
2017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概况
〔德〕苏费翔
2017年,欧洲朱子学研究成果主要展现在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会上, 概况如下:
1.2017年9月7〜9日,欧洲中国哲学学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hilosophy, EACP )第二届双年会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召开。
欧洲中国哲学学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hilosophy, EACP ) 由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University of Ljubljana )汉学教授罗亚娜(Jana S. Rosker )女士于2014年2月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创立,罗亚娜教授为首任主席。现任学会主席为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Vilnius University )东方研究中 心(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主任韦特斯(Vytis Silius )。该学会旨在鼓励并促进欧洲各国的中华哲学学术研究,为富有成效的合作与思想交流创建并提供平台,开辟亚洲特别是中华思想史方面学者之间的对话,为当前领军学者的发言 与探讨提供平台。
年会上,有关朱子学的报告主要有:
Maud M 'bondjo (卓楚德,法国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德 国埃尔朗根ー纽伦堡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Numberg ),发表论文“A Philosophical and 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date ( Ming ): The Case of Zhu Xi(1130〜1200)”(《哲学与卜筮学对“命”的解释ーー以朱熹为例》),详论朱熹对“命”概念的见解。作者综合《朱子语类》“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与《周易本义》将《易经》视为卜筮书的基本看法,分析朱子读书、静坐、卜卦的工夫,强调朱熹虽然接受大们卜筮的习惯,但是自己却极少算卦问命。
Fr6d&ic Wang (王论跃,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〇),发表论文 "The Notion of Ming in the Beixi ziyi by Chen Chun ( 1159 ~ 1223 )”(《陈淳〈北 溪字义〉论“命”》),强调“命”为《北溪字义》首段的主体,而要研究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过,王老师没有找出哲学理由,而是猜测与《近思录》的结构有 关,从而推论陈氏把《北溪字义》视为口授哲学伦理的教材。
Margus Ott (熊古思,爱沙尼亚的年轻学者)发表论文"A Deleuzian Perspective on Zhu Xi"(《从德勒兹的角度来论述朱熹》),用著名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 1925〜!995 )的本体论思想来发挥朱熹的理气论与大极思想。Christian Soffel (苏费翔,德国特里尔大学)的论文题目为"Mystical Elements in Zhu Xi's Cosmology: The Notion of 'Empty Soul-Consciousness (《朱 熹宇宙论的神秘色彩:“虚灵”的概念》)。论文以朱熹在《大学》《中庸》中出现的“虚灵”ー词为出发点,介绍朱熹把“虚灵”视为人心的特征,朱熹的弟 子(如黄榦、陈淳)进ー步加以说明,使“虚灵”成为学术专有名词。
此外,Vladimir Glomb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发表论文“After Zhu Xi: Kor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otong"(《朱熹之后韩国的道统说》),Martin Gehlmann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发表论文“Zhu Xi's White Deer Grotto Articles of Learning as Educational Philosophy"(《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的教育哲学》)等。
2. 2017年9月14~ 17 H,第二届“唐至明中国人文会议”(Second Conference on Middle Period Chinese Humanities )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
此次会议由魏希德教授(Hilde De Weerdt)和何安娜教授(Anne Gerritsen )共同筹划举办,吸引了来自欧、美汉学界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的关注,参会学者超过百人。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史 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探讨从唐代到明代的中国人文。
朱熹作为宋代著名思想家,对其思想研究者甚多:Joep Smorenburg (荷兰 莱顿大学) "Zhu Xi's Military Thought: Utilitarian Perspectives on the Jin-Song Conflict”(《朱熹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对女真金与宋人冲突的看法》),Kim Youngmin (首尔大学)-"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Theory: Revisiting Zhu
Xi's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经注与政治理论:重谈朱熹的四书章句 集注》),汤元宋(北京大学)——《〈朱文公文集〉未收书信原因考释—— 元两朝文集所见朱熹书信真迹题跋为线索》,祝平次(台湾“清华大学”)—— 《邵雍、张行成与朱熹》,任昉(德国特里尔大学)ーー《赵秉文之〈道德真经 集解〉及其学术源流》,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德国特里尔大学)—— "Reexamining the Topic of Shendu in Confucian Traditions from the 13 th Century"(《重谈!3世纪儒家学派的慎独论》)等。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蔡方鹿 赵聃
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他吸收并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思想,从而建立了“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2]此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这些思想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朱熹的思想体系。虽然理学与文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为数众多的经学家兼治文学,文学家亦擅长经学,而经典本身又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文学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3]朱熹将经学义理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点。正如钱穆所说:“轻薄艺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应共赴之标的。”[4]因此,这里很有必要清理一下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或可为朱子学提供一个“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视野。
一、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研究
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两部著作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相关问题上。另外,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朱熹理学与其《韩文考异》关系的研究。
(一)理学与《诗集传》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诗经》彻底脱去了‘经典’的神圣皇袍,而被认作是一部诗歌总集。”[5]朱熹理学与《诗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地被学界所关注。1919年傅斯年提出:朱熹的《诗集传》虽然还有几分道气,但具有“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的特点。[6]1928年他在《泛论<诗经>学》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部书(《诗集传》)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7]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一书中认为:“朱熹论《诗》,如更进一步,超脱宗教性之经学,而立场于纯文学之观点,则一切新说适足以显其伟大的创见;奈其说仍局促于经学桎梏之下,仍以伦理的观念为中心,则何怪乎责难者之纷来。而吾人于此,亦可见经学与文学自有其不可混淆之封域矣。”[8]与此同时,郑振铎也认为,朱熹“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9]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多是点到为止,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港台学者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钱穆认为:“朱子以文学方法读《诗》,解脱了经学缠缚,而回归到理学家之义理。”[10]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主要集中在《诗集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是对“淫诗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义理时,涉及“淫诗”与义理及人情的关系,这与《诗经》的文学性相关。如谢谦说:“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沟通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淫诗’之说能够在经学范围内成为可以‘自圆其说’的体系。严格说来,朱熹不是发现了《诗经》中有‘淫诗’,而是从理学角度完整地阐述了‘淫诗’为教的经学意义。”[11]认为朱熹将“淫诗”纳入了他的理学体系来阐述他的诗教思想。另外,赵沛霖、吴正岚、谢海林等对此也持相似的观点。[12以上学者认为,朱熹的《诗经》研究虽然涉及“淫诗”这一文学性的特点,但本质上朱熹是站在理学的角度来阐释《诗经》的。台湾学者姜龙翔亦云:“朱子对淫奔诗的界定虽是由其理学思想出发,否定诗人情性,进而对于民歌抒发自由情感的本质有所误解,但经由朱子的论述,却较汉学将《诗经》视为国史代言创作的产生论,表现出多元的解释。”[13台湾学者黄景进从朱熹的心性哲学出发做了研究,说:“朱子根据其心性哲学,认为情有善有不善,故诗亦有正有变,由此认定《诗经》中有‘淫诗’(淫诗所表达的是不正的感情),并反对‘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说法。”[14]
二是认为朱熹以文学解《诗》,突破了理学的束缚。美籍学者杜维明在《朱子解诗》中说:“朱熹把《诗经》视为美学思想的源泉和道德训诫的宝藏而加以认真研究。……朱熹认为在客观地分析诗以前必须朗读诗和体验诗的意境。”[15]这也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读《诗经》。莫砺锋认为:“朱熹著《诗集传》,其本意也是从事经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悟性,其治学态度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所以他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质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诗集传》在实际上终于打破了经学的藩篱,《诗经》学终于在一位理学宗师的手中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16]汪大白说:“朱熹正是在他的理学宗旨与文学意识紧密结合和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研究直接影响并实际革新了旧的经学研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诗经》学发展史的根本性转变。”[17]另外,檀作文、李士金也对此发表了相似的论述。[18]以上学者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理学思想的过程中,“以《诗》言《诗》”从而促进了《诗经》文学性的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朱熹研究《诗经》的方法是分不开的。蔡方鹿以朱熹的读书法为切入点,认为:“‘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文学的功能在于抒情,诗人言《诗》,则‘发乎情’;其理学的要旨则在于阐发义理,理学家说《诗》,不离理与性善。朱熹既重《诗》文之言情的本义,又重义理的阐发,因此可以说,朱熹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情与理、情与性的结合。”[19]并指出:“朱熹客观地看到古人作《诗》是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突出一个‘情’字,认为抒发感情和自然情感是诗人作《诗》的本意。同时,朱熹也注意把吟咏情性与玩味义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20]分析了文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郝永以《二南》为例分析了朱熹二《南》解释学中“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矛盾性”。[21]]台湾学者陈昭瑛则“尝试建构朱子的诗学及其与儒家诗学的关系”,“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脉络来掌握朱子诗学与儒家诗学的现代意义。”[22]
三是把朱熹的《诗经》学与经典解释学结合起来。邹其昌从诠释学美学思想的角度认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由‘以《诗》说《诗》’所开启,历经‘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之磨炼,旨在获得‘性情中和’之境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转折意义的典范。诗经诠释学由此逐渐走出‘经学’,走向真正的审美!”[23]即朱熹在对《诗经》的诠释中认识到了其中的文学性。曹海东认为:“就朱熹的经典解释活动看,他可以说是很好地践行了上述解释学原则。对《诗经》的解释就是一个显证。”[24]这些原则包括据诗之情实自出新解,把训诂释文义与讽诵见道理相结合,即在《诗经》诠释中,把文学与理学结合起来。郝永则系统地对朱熹《诗经》的解释学进行了研究。说:“朱熹解释《诗经》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其文学特质的重视,二是对其理学价值的发掘。两者都是对汉唐经学以美刺解《诗经》的大突破、大发展。”“故朱熹的《诗经》解释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既有文学的维度,也有理学和史学的维度;既是对经学旧说的继承与扬弃,也有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总之,朱熹《诗经》解释学是以理学为旨归的多维度的经学体系。”[25]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一角度对朱熹的《诗经》学进行研究,我们要清楚的是,理学与文学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的分类下产生的,“然若从贴近古代情状的视角观察,从前儒者的经典诠释活动,也可能透过类同文艺批评的形态发生,特别是在向以艺术性见称的《诗经》身上,朱熹的《诗集传》或者就是个典型案例。”[26]因此,我们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不能割裂其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应从理学、文学二元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和把握朱熹的《诗经》研究中理学与文学间相分相合、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理学与《楚辞集注》
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其著作《楚辞集注》一书中,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朱熹的《楚辞集注》展开。朱熹的楚辞学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有学者认为:“朱熹最早彻底地以文学眼光看待楚辞,他自觉抛弃了楚辞研究中的经学标准,抓住了楚辞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27]也有学者认为:“朱熹在鉴赏楚辞的时候,的确是把‘情’字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只要理智稍胜感情,便要流露他道学面孔,立刻会对情字加以限定词,要求情必须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28]实际上,朱熹的楚辞研究并没有抛弃经学、理学的标准,这一点学界多有讨论。韩国学者朴永焕认为:“朱熹在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理论基础上,主张实行以道为本的判文、以理为准的评诗、以古为法的复古思想。”[29]并且这些文学思想强烈地影响了《楚辞》的研究。束景南也认为朱熹在注解《楚辞》时“用理学的‘文化范型’重新铸造屈原的历史形象”并“把作为游艺之学的文学也拉回到理学的轨道与框架中去。”[30]孙光从篇目选择和体例确定、文本注释、屈原思想的阐发、楚辞艺术的观照、注释特点五个方面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的关系。他认为:“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使其在注释中既遵循理学价值标准阐发义理,又能够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31]罗敏中从朱熹的“尊屈倾向”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32]李士金则研究了朱熹将理学思想引入楚辞研究的原因,认为:“朱熹把他的理学思想引入《楚辞集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南宋科技水平进步之结果。”33另外,还有学者对朱熹的辞赋观做了研究。何新文认为:朱熹的辞赋批评“明显具有以道德哲学标准否定文学的偏见。”[34]这在注释篇目的选取上也有体现。莫砺锋认为《楚辞后语》对作品的选择受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理学家的迂腐性。[35]于浴贤、徐涓、台湾的梁升勋对此也做了考察。[36]虽然以理学的标准来选取篇目确实会遗漏一些好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就此来研究朱熹的辞赋观和文学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学者,多从朱熹的理学思想出发来论述理学对朱熹楚辞学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理学阐释方法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肖伟光认为:“《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37]徐涓从格物致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格物’结果是‘物格’与‘知至’,亦即求得事物义理之豁然贯通,对《楚辞》而言,就是兼得其‘性情’与‘义理’。”[38]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集注》及楚辞学关系的研究多从理学对楚辞学的影响着手,而很少注意到《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对于朱熹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朱熹在评价《楚辞》时多是义理性与文学性兼有的。如据《楚辞集注》载:“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39在这里,朱熹把阐发君臣之义理建立在承认《楚辞》“陈情”感怀之言情性的基础上,可见文学对理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朱熹《楚辞》学的研究,不能忘记朱熹理学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和朱熹《楚辞》研究理学与文学兼顾的特点,应从理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入手,找出二者的联系。
(三)理学与《韩文考异》
对于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的研究,学者们多把《韩文考异》当作朱熹校勘学的代表而研究其校勘学意义。吴长庚认为:“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法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40]朱熹的《韩文考异》中确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但朱熹并不是为了校勘而校勘,他是借助韩文的校勘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的。正如钱穆所说:“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然则校勘虽小业,于义理经术史学文章靡不有其相关互涉之处。后人仅知从事校勘,又何能望其津涯,而窥其底蕴。”[41]可见,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束景南认为:“朱熹在党锢中选择韩愈文集做考异的目的又不仅是为了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个大文豪的威望来巧妙宣扬‘道学’的深意。贯串在《考异》中对韩愈批判的一面,便渗透了他的道学‘伪气’。”[42]
二、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研究
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有文道观、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等四个主要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如蔡方鹿、王哲平等。蔡方鹿认为:“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道合一,‘即文以讲道’和诗理结合的思想。其理学与文学并行不相悖,可以互相结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与只重理学而轻视文学的理学家相异,同时也表明理学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文学的桎梏,尽管理学有抑制文学的倾向。”[43王哲平从文学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做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44]李春强则从理学著作《论语集注》出发综合研究了朱熹的文学本体观、创作观等文学理论。[45]
(一)文道观
张立文指出:“文道关系论是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文道关系论的展现,便是诗与理的关系。”[46]台湾学者杨儒宾也认为“朱子说‘道之显者谓之文’,‘文’与‘道’可视为一体的表里关系,这当视为理学家另一种对文学重要的界定。”[47]可见,朱熹文道观也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对于这一论题,学界的主要看法是“文以载道”或“文道合一”。“文以载道”论以周予同为代表。他说:“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亦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如皮附以今日流行之文学术语,则朱熹或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48]此外,朱东润、陈千帆、台湾学者张健、钱穆等都持相近的观点。[49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持“文道合一”论,他认为:“文学不是‘道’的从属物,而是持有自身根据的自立之物。文学存在着自律性,植基于‘气’(气象)的发动,在这种根源性中文与道合成一体。”[50]吴长庚认为:“文道合一是建立在文与道二者并重,各不偏废的基础上,并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总结。”[51]对此莫砺锋、吴法源也持相同的观点。[52束景南进一步认为:“朱熹通过曾巩融合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学问路数,统一了道统与文统。”[53]值得一提的是,程刚从“理为太极”的太极观出发来讨论朱熹的文学本原论,认为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本论的哲学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一方面延续了文从道出的本原论,以文为工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于程颐‘作文害道’的一个修正。”[54]
(二)理学与诗论
郭绍虞指出:“朱子论诗不唯集道学家之大成,也且兼诗人之诗论而有之了。”[55]对于朱熹理学与诗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理学思想对其诗论的影响上。一般认为,朱熹诗论的基础态度是“道学是第一义的当行职责,做诗是第二义的感情辅助”,“诗歌的首要第一条便是义理纯正,所谓‘诗以道性情之正’。”[56]马积高亦认为,朱熹的诗论“强调诗人的主观动机要合于所谓‘性情之正’才行。”[57]以上学者的观点都看到了理学对于朱熹诗论的影响。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进一步认为:朱熹“以儒家心性理论为基础的诗歌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要求诗歌创作将情感体验与性理规范统一起来,成为作者道德人格和高远胸襟的流露,具自然平淡的‘中和’之美。”[58]石明庆讨论了朱熹理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影响其诗学的主要有理本气具的理气论、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居敬穷理的工夫论,以及心与理一的境界论等理学思想。”[59]另外,台湾学者黄景进从美学的角度对朱熹诗论进行了研究。他说:“大体而言,当朱子在论《诗经》时,他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发挥儒家传统的诗教观为目的;而当他在评论历代的诗人时,却较注意诗人在美学方面的表现。”[60]
以上学者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楚朱熹理学思想影响下的诗学理论。这也启发我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评价朱熹诗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宋代理学家诗论中最有价值的”,“他论诗的许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珍视,其保守的一面则应予以扬弃。”[6[
(三)理学与古文理论
对于朱熹理学与古文理论关系的研究,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台湾学者何寄澎认为朱熹文论的“一切观点(包括文学性的观点)悉以道学为归趋。见证了朱子文论一方面是更道学化的;一方面却又是更包容而圆融的。”[62]闵泽平认为:“朱熹的文章理论虽带有浓厚的道学色彩,其间却颇多精辟的见解。他也重道轻文,但其观念远比周、程等人通达。”[63]
(四)理学与作家作品批评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除以上三个方面外,也有学者对朱熹的作家作品批评进行了研究。如踪凡认为:“朱熹论两汉诗赋,手中拿着两大标尺:一曰道德,二曰真实……他由此出发而得出的扬贾抑马,尤其是贬斥扬雄的结论尤其让人不能信服。”[64]全华凌论述了朱熹以“道”来评价韩文的得失。[65]黄炳辉认为朱熹的唐诗批评其精辟处在于道学和文学的统一,其瑕疵处“是以道学家的眼光代替诗艺术本身的观察。”[66]莫砺锋对朱熹的作家人品批评做了研究。认为:“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极为关注作家的品德修养。”[67]李士金则对此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朱熹“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68]谢谦全面地考查了朱熹的文学批评,他说:“朱熹正是根据这一新的价值标准,对《诗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的阐释与评价,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批评的模式。这个‘以理说诗’的道德批评模式同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史证诗’的历史批评模式一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69]以上学者研究的多是朱熹理学对某一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虽然不乏深刻的论述,但却缺乏系统性。另外,学者们多关注的是朱熹理学对其文论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文学理论是他理学思想的反映,及朱熹文学思想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在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某一文学理论,较少系统地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很少讨论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作为朱熹文学思想基础的文道观对他的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
三、朱熹理学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
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之史学与文学》一文中指出:“朱熹之文学作品,诗赋散文,各体均有。然韵文喜插入说理之语,每使人深感酸腐之气……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70]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诗歌与文章创作两个方面。
对于朱熹诗歌创作的研究集中在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上。胡明认为:“朱熹作为一个道学家,他的诗却绝少道学气,更无头巾气、酸馅气。”71郭齐认为:“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72]许总对朱熹的创作实践做了分析,认为:朱熹的创作实践“即使是为了说明治学之理,亦全借优美的自然意象表达出来。正因这类‘不腐之作’,朱熹诗被后人称为‘道学中之最活泼者’”[73]。莫砺锋亦认为:“朱熹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丰富生活情趣的诗人,这种独特的素质使他成功地消除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并进而使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74]李育富研究了朱熹易学思想与其诗歌关系的互动,说:“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75]吴长庚则“从朱熹解易解诗之思维程序、方法、原则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朱熹的解诗思维中,他致力于诗歌比兴形象的发掘,寻求诗歌感发性情的活的功能,力求通过正确的诗解,建立一套开放性的解诗思维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易解思维中之积极成分的”。[76]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朱熹诗中的理学思想。美籍学者陈荣捷在《论朱子<观书有感>诗》一文中解释了诗中词语的理学含义。[77韩国学者李秀雄认为:“朱熹作诗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诗本身的艺术形象。他使诗中的理和趣互相和谐而达到交融的境界。”[78]日本学者申美子在《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朱子数量庞大的诗作,正是研究其一生思想形成、转变、发展极其丰富而真确的材料”,并从朱熹的诗作出发,“探讨其一生学问思想的发展轨迹”。[79]石明庆也认为,朱熹的诗歌“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80]。在朱杰人看来,“朱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抑或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对宋代的诗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公正的、充分的估价”[81]。胡迎建亦云:“了解其理学与诗歌的关系,有利于理解其诗。”[82]这同样也能进一步了解朱熹的理学思想。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章创作关系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饶宗颐对朱熹的文章做了研究,认为“朱子说理之文,逻辑性特强,又覃思者久,增、减不得,极得洗伐工夫”[83]。莫砺锋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他(朱熹)的散文写得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他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理解理学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窗口”[84。而闵泽平则深入地探讨了朱熹理学与其文章创作的关系,认为“朱熹行文的从容、平和,首先来自于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对义理的体认与把握,来自他道学气象的自然流露”[85。方笑一将朱熹的经学与文章之学相结合,认为:“与北宋儒者不同,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86另外,王仕强认为:朱熹“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87]具有典范意义。黄拔荆、周旻则“分析了朱词与其文学观、理学观的关系”[88]。许总则对朱熹理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说:“朱熹将‘义理’与‘诗文’加以遘合,表明了对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89]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明了理学对朱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以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的朱熹的文学作品。另外,通过分析研究朱熹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究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理学与文学是怎样融合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这也是朱熹文学作品对于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特殊意义。
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展望
通过以上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是开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学与《诗经》学、文道观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但研究成果多为简要的概括式论述,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港台及海外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虽然百年来学术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以至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比较而言,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进行,尚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做出一个融会贯通、整体综合性的系统研究。由于朱熹思想本身就是由文、史、哲,儒、佛、道等相互贯通而构成,朱熹理学与文学是统一于朱熹思想的一个整体。因此,研究朱熹理学不及文学、研究朱熹文学不及理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一些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某一方面的文学做过个案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作为整体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故未能揭示出朱熹理学与文学之总体特征,因此也不能进一步说明朱熹理学与文学之关系。所以目前的研究情况与朱熹既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尽管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目前的研究,确实是朱子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需要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高。在这个新的视域下,去挖掘朱熹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实质及所体现的朱子学的特点,而不是以往大多就事论事地分论朱熹的理学和文学,从而澄清和阐明朱熹理学思想中的文学性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回答其理学怎么通过其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而其理学思想里又具有哪些其他理学家不曾有的文学性等问题?从而客观揭示朱熹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及情理结合的特征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既对深入研究朱熹理学有利,也对深入研究朱熹文学有利,更对全面、综合研究朱子学有利。因此,站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朱熹思想及其价值、地位和影响,对于学术界完整理解朱熹的整个思想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我们以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为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进而展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开展:
(一)朱熹思想是在致广大、尽精微,涵盖、吸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打破界限,以融会贯通的视角去研究朱熹思想。这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学科学术研究之间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时代要求。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将朱熹的理学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仅以此促进朱子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而且拓宽了研究领域,这对朱子学的研究很有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应将具体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由于朱熹文学是由《诗经》学、楚辞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等多方面构成,我们应以这些具体的研究为基础,运用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散到联系、从局部到整体的观点和思路,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展开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并加以概括提炼,从而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系统的认识,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文化史上伦理与自然之争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尚伦理、重教化与崇自然、重情感两种文化价值观之争,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对其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其理学思想中的尚伦理、重教化与文学思想中崇自然、重情感是怎么统一于朱熹思想中的,它们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的融合又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研究的展开将为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创新的视角,同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儒学与文学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及所体现的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亦是朱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所要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某一学科的创新。某一理论学科的成就,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先导。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应采用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融合互动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上,应采取点、面、线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置于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以朱熹理学与文学为点,以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和盛行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为面,以整个中国经学史、文学史、理学史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结合,在相互联系中,做纵横比较,分析探讨,深稽博考,融会贯通,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在中国经学史与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和作用。
(四)在研究工作中,应将理论分析与训诂相结合。既要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把研究建立在考证、训诂、细读深研文本,弄清掌握朱熹经学、文学著作本义的基础上,又要避免单纯的训诂考证,而忽视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及其思想性的深入、深刻表达。
以上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仅是我们的一点意见。希望通过以上的评述和论析,在以往研究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拓展,站在朱子学促进、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时代高度,以创新的方法、理论和新视野、新材料的挖掘运用,为朱子学的研究,在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影响、结合的视域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展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世纪以来张栻思想研究述评
蔡浪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当时学者陈亮评价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1]“荆州”即是指张栻,故又有“一代学者宗师”之赞誉。张栻是1160年左右最有影响力的道学家[2],在老师胡宏去世后,成为湖湘学派领袖,使湖湘学派思想发展成熟,造就了“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3]的盛况。《宋史·道学三》卷四百二十九[4]中将张栻和朱熹两人并列一传,肯定了张栻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一直是既热门又重要的研究课题。张栻对朱子学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在朱子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陈来先生曾说:“张南轩是朱子学前期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5]然而,对于张栻的研究,却长期被学者所忽视。整体而言,作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学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张栻在日美韩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大陆关于张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虽然目前对于张栻的研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很大拓展和进步空间。现就张栻国内外研究概况、生平与评价、交游、理学、经学、实学与教育、回顾与展望等方面,对20世纪以来张栻思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并略加评述。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在日本宋明理学界研究中,张栻乃至湖湘学研究,皆属于边缘化课题。对张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高畑常信先生表现最为突出。高畑常信先生师承友枝龙太郎,专注于张栻以及湖湘学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了有关张栻《论语解》、张栻思想的变迁、与朱子论未发已发以及仁说等思想研究的成果。1996年,高畑先生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出版《宋代湖南学の研究》[6]一书,这是日本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研究湖湘学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少有人再专门从事张栻思想研究的工作。从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日本的研究者们比较专注于从思想史及文献学的角度,对张栻的思想进行史料翔实的考辨以及细致的文献梳理,但在义利的诠释方面却有所欠缺。
在欧美,对张栻包括整个宋代思想研究,与汉学其他领域相比,呈现出起步晚、相对边缘化的状况。蔡慧清对欧美的汉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认为长期以来,欧美对传统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后延伸至秦汉,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西方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朱子学在内的西方宋学研究才逐渐繁荣起来。[7]有关张栻思想的研究,亦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才逐渐走入美国学者的视野。陈荣捷先生对打开美国宋学研究的新局面贡献显著。陈先生在对朱子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中,也涉及了对张栻的研究,却并未对张栻的思想价值与贡献做出其应有的评价。田浩先生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外在进路”的研究方法入手,在研究朱子的同时肯定张栻对道学形成的重要贡献,为国内学者研究张栻乃至朱子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切入点。虽然这些学者的努力,推动了张栻思想研究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南轩学作为朱子学研究下的一个边缘化课题的地位,在欧美国家并没有改变。
韩国学者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相比之下更少,还未出现过对张栻思想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多是在研究其他人物或问题时涉及。对于张栻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与朱熹联系在一起,涉及主题包括中和说、仁说、工夫论等。
在中国台湾方面,以往对于南轩学乃至湖湘学并无过多关注。湖湘学研究之所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要归功于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先生将宋明理学分为三系:伊川、朱子一系,陆、王一系,胡五峰、刘蕺山一系。[8]这大大提升了湖湘学的地位,以胡宏为首的湖湘学由此被重视起来。虽然牟先生将张栻排除在其分系之外,但毋庸置疑,张栻在湖湘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湖湘学不可回避的人物之一。于是,由于对湖湘学研究的逐渐关注与重视,张栻思想的研究也随之而展开。总的来说,牟先生对于张栻的否定,消解了张栻在南宋思想史上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张栻研究在台湾不被重视的基调。尽管这一局面在现在有所改变,但并无根本性的改观。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80年代初,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展开研究后,在受重视程度、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皆得到了迅速发展。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向大会提交专论张栻思想的文章,从各个侧面对张栻的生平学术活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张栻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张栻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9]这表明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已进入宋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并初步对张栻思想进行了探讨。
1991年蔡方鹿先生《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1]一书出版,弥补了学界张栻研究专著的空白。紧接着陈谷嘉先生《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11]出版,该书在理论论述上深入细致,其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湖湘文化的弘扬,并且将张栻放在与朱熹齐名的位置来谈他对理学的贡献,颇有为其理学地位正名的意味。由于这两本书的出版,张栻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
进入21世纪,对张栻的研究更是发展迅速。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四篇专门研究张栻的博士论文,分别是:苏铉盛《张栻哲学思想研究》[12],王丽梅《张栻哲学思想研究》[13],邢靖懿《张栻理学研究》[14],吴亚楠《张栻经学哲学论》[15]。苏铉盛和王丽梅皆是针对张栻的哲学思想,前者从仁说、中和说、心论、性论、敬论、知行论和义利之辨等问题入手,后者则从本体论、工夫论、人性论、义利观、知行观等传统框架来展开论述。邢靖懿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张栻的理学思想上,增加了对张栻经世思想以及排佛辟佛思想的阐述。吴亚楠则从经学和哲学结合的角度,对张栻的经学思想进行分析,重视他的思想中经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这些博士论文皆是研究张栻的专门成果,代表着张栻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会议论文集《张栻与理学》[16]和《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17]的出版,亦大大地丰富了张栻的研究成果。
此外,《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一书,将张栻经学与其理学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不仅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而且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18]而杨世文教授点校的《张栻集》[19],是现在最完整的文集版本。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张栻年谱》[20]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1]两本书。这两本书进一步弥补了张栻研究材料之缺。丰富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新材料的补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张栻生平与事迹,有助于张栻交游等研究开展,预示着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在未来将步入新的台阶。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张栻作为朱子学前期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重视。美国学者田浩虽然注意到了张栻的重要地位,但并没有改变张栻思想研究在欧美宋学研究中的边缘化地位。大陆对于张栻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其重要性得到大大地提升。但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和同期的朱子和吕祖谦存在差异,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生平和评价
研究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源流、学术传承以及影响与评价等相关信息,不仅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亦是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人物生平与评价的把握,更有助于思想研究的开展,以及更客观、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内容。
(一)生平事迹
朱熹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22],所载张栻传记翔实可靠。张栻的年谱比较晚出,一直到清道光年间宁乡王开琸辑刊《南轩公年谱》,才弥补了这一空白。另外还有民国时期胡宗楙编撰《张宣公年谱》,日本学者高畑常信的著作《张南轩年谱》,亦可供研究者参考。如今,这三本年谱由邓洪波教授辑校为《张栻年谱》[23],书中同时辑录了有关张栻的画像、传记、祭文、著作提要和序跋、纪念书院资料等文献,为学者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张栻提供了基本条件,为张栻思想研究带来了便利。
(二)学术源流与传承
胡昭曦先生对张栻的学术源流进行了系统清理。他认为张栻的学术师承主要是胡宏,除此之外还有孙复、司马光、邵雍、苏轼、谯定、张浚的学统,由于这种多元的师承,张栻在学术上得以集诸家之大成。其次,张栻的学术,植根于蜀,成熟于湖湘,其学术是蜀学和湖湘学的结合与发展。另外,张栻之学,经过他在蜀中的弟子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从湖湘返传回蜀,使正在继续发展的蜀学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学者,促进了蜀学的再盛,这是当时宋朝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
目前学界对于张栻学术渊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周敦颐、胡宏以及家学的继承与发展上。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鼻祖,在理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周建刚分析说,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发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周敦颐“道统”地位的强调;二是撰《太极解义》,从“太极为性”的角度诠释周敦颐的思想。[25]张栻师从胡宏,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郭齐认为张栻在接受胡宏思想时,不固执一隅,采取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26]钟雅琼分析指出,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27]家学亦是张栻思想来源的一部分,他一生陪伴在父亲张浚身边近30年,启蒙、受学乃至仕途皆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金生杨对张栻如何继承、扬弃张浚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释,认为透过张栻对张浚学术的继承与扬弃,我们更能体会张栻学术融会、由粗转精、由杂转醇之功。[28]
至于学术传承方面,张栻对湖湘学以及蜀学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对张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29]的评价,奠定了大陆学者评价张栻对湖湘学派作用的基调。陈谷嘉先生指出,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他对湖湘学派的发展无论从理论的发展,还是从传播湖湘学派的学术,皆贡献最大,他是继胡宏之后的唯一巨匠。30除了湖湘学以外,张栻亦是宋学中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夏君虞先生所说,他乃“蜀学的基石”[31]之一。杨东莼认为“南轩之学,盛行于湖、湘,流衍于西蜀”。[32]胡昭曦指出,南轩之学返传回蜀,推动了宋代蜀学的转型、“洛蜀会同”和宋代蜀学发展第二个高潮的形成;在南轩之学返传回蜀的过程中,宇文绍节、陈概、杨知章起到了倡导作用,其主要据点是沧江书院,而二江诸儒则是返传南轩之学的主力学者群。[33]
(三)影响评价
张栻“是否继承师说”“是否从朱熹转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一直是评价张栻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学者多认为张栻继承了师说,肯定张栻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全祖望早就指出:“张栻从朱熹转手,就好比说张载是从学二程一般,其实出自朱子后学捏造,不足为信。”[34]钱穆先生认为,“二人去短集长,交相师益,不必定说谁跟了谁。”[35]陈荣捷亦承认“南轩之于朱子,的是切磋琢磨之益友”。[36]蔡方鹿教授对张栻在哲学和理学上主要贡献的总结,代表了研究者们典型的看法。具体而言,主要贡献有三:(1)确立了集众家之长的湖湘学派;(2)在与朱熹的相互辩难中发展了二程学说;(3)论述并丰富了宋代理学的一系列范畴和重要理论。[37]不过亦存在不同的看法。牟先生认为张栻由于“受教日浅”,“未能精发师要,挺立弘规”,于朱子也“毫不能有所点拨”。[38]其弟子蔡仁厚先生进一步发挥师说,认为“南轩实乃五峰之不肖弟也”。[39]曾亦教授则认为,学术界素来认为南轩之学术因受朱子影响而发生改变,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40]
客观地说,1180年张栻英年早逝后,其在理学上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再也无法与朱熹相比拟。张栻学说后来之所以式微,李可心从心的出入问题加以观照,认为张栻的学术风格缺少应有的主动性和创发性,兼有理学和心学的特征而欠充分,且更偏重于实践性,以致逐渐丧失了在理学内部的话语权。[41]对于张栻在后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李英镐的一篇题为《吸收南轩学而产生之寒冈学的新理解——以寒冈郑逑的论语学为中心》[42]的文章。该文认为寒冈郑逑在重新诠释《洙泗言仁》的过程中,有吸收张栻的思想。这意味着张栻的思想对韩国思想家亦产生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其海外影响力,有待我们的发掘和研究。
近年来,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让学界开始重估张栻的地位和影响。田浩先生把“道学”的形成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二阶段把张栻、吕祖谦、朱熹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考察,认为他们的交往加速了道学传统的形成。[43]在具体时代背景下对张栻思想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考察后,田浩先生认为张栻对朱子的影响与贡献比以往学者想象的还要大。[44]这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张栻在道学乃至整个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张栻的思想研究也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发展。
三、张栻交游研究
与其他学者的交流和沟通,是张栻思想形成与完善的重要因素,道学亦是在这种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中形成的。书信是研究张栻交游最直接的研究资料。在书信编年上,杨世文、任仁仁以及顾宏义等学者,皆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仁仁和顾宏义两位学者,对张栻与同时代学者往来的书信加以汇编,考证其撰写年月,有益于南宋前期学术史、政治与党争研究、学人间交游情况等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5]杨世文教授除了对张栻写与朱熹的书信进行编年考证外[46,还对张栻诗文中关涉的若干人物进行了考证[47],这对于张栻诗文编年,以及张栻年谱的编纂,乃至研究张栻学术交游、学术思想演变皆有帮助。张栻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游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朱张二人的交往,另外还有些许有关东南三贤以及其他蜀学学者往来的研究。
(一)张栻与朱熹交往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山口察常于1938年发表了《朱子と张南轩》[48]一文,率先对朱子与张栻进行了考察。张栻与朱熹的交往研究,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张栻的交游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篇幅。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两人交往历程、朱张会讲、思想异同等方面。
综观张栻与朱熹的一生,两人仅有三次会面,其他皆以书信往来为主。陈代湘教授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49]
朱张会讲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世,开书院会讲制度之先河,成为书院自由讲学之先声,很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肖永明和谢川岭两位学者考察了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的变化,认为这样一种叙述事实的变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这种考察,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50]李清良和张洪志两位学者对“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进行了阐释,“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1]
在对张栻与朱熹交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是围绕两人思想争论进行的。陈谷嘉先生认为张栻和朱熹的个体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本体论上的分歧和争辩,二是中和之辩,三是仁说之辩。[52]陈代湘教授则认为朱熹与张栻二人思想存在异同,他们相同之点表现在性之善恶问题、心性关系,对仁的解释以及涵养识察之先后问题上。二人观点相异之处则表现在对太极的解释,对心的主宰性上。[53]田浩教授认为南宋道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朱熹的道学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他与张栻间气氛和谐的学术讨论中。在此,他选取了其中对道学同道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第一,工夫修养与“中和”问题,第二,《胡子知言》的讨论;第三个主要问题是“仁”。[54还有许多学者对张栻与朱熹之间关于太极、中和仁说以及察识涵养工夫论等思想展开了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些将在“哲学理论之探讨”一节阐述。
(二)东南三贤以及其他学者往来的研究
朱熹、吕祖谦与张栻在南宋并称为“东南三贤”,三者均为二程后学,他们的师承渊源有着密切关系。田浩先生对朱熹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论述,强调朱熹之外的同时代儒家的重要性。[55]潘富恩先生对三人理学思想之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人思想上的异同,与二程有关。三者尽管学术各自有所偏重,亦有所分歧,但毕竟基本倾向是一致的。他们在互相切磋的过程中,都各自受到对方的启迪,增进了知识,使理学臻于精密、博大。对理学的发展,“东南三贤”各有自己的贡献。[56]此篇文章,后被高畑常信翻译成日文出版[57]。刘玉民指出,张栻与吕祖谦于《胡子知言》《论语》《孟子》《易传》《阃范》《仁说》等皆有学术交流,并于商榷中互相指正,切磋中互相提高。[58]
在与蜀地学者的交游方面,钟雅琼依时间先后之序,亲疏之别,论述了张栻与蜀地学者史瑶弼、宇文氏、范氏、丹棱李氏以及陈概等的交游情况,认为他的学术是理学与蜀学相融的前奏,他本人也在无意之中为“洛蜀会同”提供了助力。[59]此外,在张栻与南宋旧儒的互动中,邹锦良认为周必大和张栻的“知行”辩论反映了南宋时期旧儒学与新理学之间的歧异互动。[60]
四、理学理论之探讨
张栻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深,就理学特点而言,张琴认为张栻的学说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以太极为枢纽、以心为核心的由形上之本体世界向经验的现实世界展开的系统,其理学思想条理清晰,主旨鲜明,在理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在宋代理学运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61]在对南轩理学贡献褒奖之余,亦有批评的声音。郭齐认为张栻由五峰而直接周程,笃守有余而发明不足,略本体而详工夫,纯宋学而鄙汉唐,宽厚而少批评,稳定而少变化。[62]目前,学界对于张栻理学理论的探讨,概而言之,主要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以及伦理观等四方面展开。
(一)本体论
陈谷嘉先生指出,张栻构制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等为基本范畴的具有层次性的本体论逻辑结构体系。[63]太极是张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其目的是为儒家伦理道德寻求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的根据。由于各种原因,张栻《太极解义》佚失不传。20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首先发现了《太极解义》逸文[64],为太极思想之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鲜为学界重视。直到21世纪,苏铉盛[65]、苏费翔[66]等学者皆对《太极解义》进行过辑佚与还原。目前,《张栻集》中附有复原的完整版张栻《太极解义》。[67]至于张栻太极说的具体内容,苏铉盛从张栻所著《太极图解》以及有关太极思想的种种观念和认识入手,对张栻太极说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其太极说之核心是以性释太极。[68]张栻之所以提出“太极即性”的命题,吴亚楠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69]李丽珠则认为两者在解经方法上存在不同:张栻以为阐述纲领即可,朱熹则以经学训传的方式系统注解其著作《太极图说》。这样一种理解基点上的差异,是朱熹与张栻对《太极图说》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70]
(二)心性论
向世陵先生认为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71]张栻与朱熹的论辩中,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心性论展开的。成中英先生通过讨论朱熹与张栻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辩,概括了孟子以来心性之学的演变发展,提出了“心之九义”说:心的本体性、活动性、创发性、情感性、知觉性、意志性、实践性、统合性和贯通性。[72]以下将对张栻与朱熹讨论频繁的中和说、仁说等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中和之辩是张栻与朱熹讨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苏铉盛对中和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叙述了从二程经过胡宏到张栻和朱熹等宋代理学之中和说,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察识涵养说之发展脉络和含义。考察了南轩早期中和说即先察识后涵养,与晚期察识与涵养并进的不同观点,及其在思想变化过程中与朱熹的交往情况。[73]
“仁说”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理论构成部分,亦是儒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苏铉盛指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造成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74]向世陵先生则认为张栻不认同“天地以生物为心”,重视“复”在天地生物和德性修养中的价值。天地之心落实为人心,重在将天地之心与人心和仁德统一起来。[75]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76]有关张栻“仁说”的考证,亦是研究其“仁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家星教授就朱子与张栻“仁说”研究中争论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仁说》为南轩本人所作,朱、张“仁说”并无“胜负”之分,二贤在切磋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77]赖尚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做了进一步深入的考证,确定了二人《仁说》的成书时间。[78]两人所作《仁说》时间的确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二人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历程。
(三)工夫论
察识与涵养工夫是张栻中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丽梅对张栻的工夫论做了集中研究,认为张栻的工夫论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不同的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其工夫论正是在与朱子不断地交涉与论辩中逐渐形成的。[79]另外,张琴对张栻的“格物致知”思想亦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在设立性与太极为宇宙与道德本体的前提下,张栻凸显了心的“主宰者”地位,强调“虚灵知觉”之心对于性情的表达与彰显。张栻将格物致知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心与“物”交往、认知与实践的完整过程。由此,他建构了颇具心学特点的“有诸己”的格物论,格物致知的关键并非外于心体的事物与事物之理,而恰恰须落实于此心物交往过程中的心体。[80]
(四)伦理观
伦理道德观是张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张栻涉及伦理的理欲之分、义利之辨以及孝悌观,皆有所研究。邹啸宇指出,义利之辨系南轩理学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关涉其整个学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等重大问题,而其实质也即是理欲之辨。南轩从“意之所向”即行为的动机处,以顺性之“无所为而然”与逆性之“有所为而然”十分精微地辨析义利之分、理欲之别,并且在存天理遏人欲的工夫论上,力主以“反躬”为本,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备受朱子、真西山、杨诚斋等学者的称颂和尊崇,对宋代理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81张栻在义利观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和贡献。粟品孝认为义利观是张栻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精粹,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卓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甚至可以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说相提并论。[82张利明则指出义利观有以下几点现代启示:(1)在经济领域,防止见利忘义;(2)在政治领域,防止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3)在文化领域,防止急功近利,杜绝重利轻义。[83]舒大刚教授从“忠孝传家,世生贤达”,“仁以孝悌为本,孝以爱敬为实”,“政治以励俗为本,劝俗以孝悌为要”等三个方面,初步考察了南轩孝悌观的内容,弥补了南轩孝悌观思想研究之阙。[84]
五、经学思想研究
张栻的经学作品主要有《论语解》《孟子说》以及《南轩易说》这三部。对于张栻经学思想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三部著作上,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到张栻的礼学和诗经学。蔡方鹿教授指出,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85]
(一)四书学
肖永明教授认为张栻对《四书》思想资料非常重视,《四书》是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其本体论、人性论、义利观、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的建构,是与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6]
在张栻的著作中,《论语》最为晚出,代表着他成熟时期的思想,是研究其经学和理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论语解》的解经风格上,肖永明教授认为张栻的《论语解》具有宗奉二程、创造性的阐释以及鲜明的理学色彩等特色。[87]吴亚楠以《论语·学而》的注解为例,对张栻与朱熹的解经理路进行了比较,指出张栻《论语解·学而》具有重理重行的特色,朱熹《论语集解·学而》具有兼采汉宋的特点。[88就《论语解》阐发的具体思想来说,唐明贵认为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读,认为张栻提出了变化气禀之性以复其初的思想、“居敬主一”的工夫论;阐发了相须并进的知行观、义利观。[89]
张栻一直很重视《孟子》的讲授,《孟子说》亦是其后期完成的代表作品。郭美华教授指出,孟子的道德哲学有两个基本概念,即本心(良知)和善。张栻对孟子本心的解释,虽然常有着不彻底性和模糊性,但其以无蔽论本心,从源初自然绽放到强调本心实现自身的整体性与过程性,从心物、心身以及人己关系的统一论本心的实现,到强调善是基于个体力行而自为肯定的实现,彰显了一条拒斥抽象思辨及虚构精神本体而强调力行的理解道路。90德国学者施维礼以张栻《孟子说》中《万章上二》的诠释为例,认为张栻能够把过去历史事件、孟子对此事件的分析、后人的注释以及其他文献的数据做一个合理的统合,这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得以保证的原因所在。[91]
(二)易学
《南轩易说》是张栻易学的代表作,目前所存的版本皆有缺失,杨世文在《张栻集》中对《南轩易说》进行了完整辑佚[92]。对张栻《南轩易说》的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初才陆续出现专门的研究。蔡方鹿指出,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93]在论及《南轩易说》的解经风格时,章启辉认为张栻《南轩易说》于时贤先贤皆有承接,在趋时而主义理易学的同时复归《易传》理路:义理本于占筮,基于象数;在回归《易传》理路的同时又异于朱熹:以象为体,数为用,器为体,道为用,为其学术的经世致用确立易学基础,提供易理依据。[94而对于张栻与朱子在易学解经风格上的不同,杨朗说得更详细。他认为在朱子《本义》中,象数与义理得到了一种综合的处理,并小心翼翼地维持住两者的平衡,朱子要协调好两种不同目视所构造的图景,张栻的《南轩易说》则着意地保持与宋代象数易的距离。[95]
(三)礼学和诗学
张栻在礼学和诗经学方面,并没有成系统的著作,但在文集里边亦有零散的论述,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对于张栻礼学和诗经学的研究,虽不是张栻思想研究的主流,亦有学者对此做了研究。在礼学方面,殷慧从以理论礼、以礼为学、以礼为教等三个层面探讨了张栻的礼学思想。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96在《诗经》研究上,张栻虽无有关研究专著,但其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叶文举认为,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97]对于“学者之诗”,学界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陶俊则主张辨证看待“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98]
六、实学与教育思想研究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倡导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反对“空言”的实学思想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振纲和邢靖懿认为,张栻注重把性理哲学与经世致用、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故避免了流于空谈义理、空疏无用的弊端。张栻经世致用的学风,泽被后世,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近千年,至今广为流传。[99]
(一)异端观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时代大背景下,张栻对待佛教持极力排斥态度。正是对佛老等异端的批判,张栻提出了经世致用和求实求理的实学思想。李承贵认为张栻对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主要表现为:对涉佛、嗜佛、传佛的儒家之批评,对佛教某些教理教义之批判,提出“反经”“固本”以消除佛教观影响之策略等三方面内容。[100]刘学智指出,张栻从儒佛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片面性和对佛教理论了解不够深入的思想弱点。[101]蔡方鹿和胡长海对张栻的“异端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辞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102]
(二)社会政治思想
作为一位理学家、政治家,张栻在继承儒家政治思想以及积累的许多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治道、治术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治国理政主张。邹啸宇从体用的角度考察了张栻的经世思想,阐明其政治哲学建构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有三:内圣与外王相倚相成的内圣外王关系;“仁心为体,仁政为用”的为政理念;“体用兼备,本末具举”的为政之方。[103]张建坤则认为张栻从天道推衍人道的生民政治理路,其内涵包括“立君为民”“君臣共治”和“养民教民”三个层次,三者共同构成了君—官—民和谐一体的理想社会政治图景。[104]蔡方鹿先生近年对来张栻理学思想的社会价值研究,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105]经世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包含着的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以骄矜为乐”的享乐主义、“从事于奢靡”的“四风”加以反对的思想,即使对现代社会纠正不良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106]
(三)教育思想
对于张栻的教育思想研究,目前最新成果是张建东《传道济民: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一书。该书是从史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写作的第一部专门研究张栻教育思想、教育贡献的著作,填补了张栻教育思想研究的若干空白。张建东以张栻的“传道”“济民”等活动和事迹为中心,充分借鉴社会史、生活史、身体史、心态史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深切关注到张栻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家庭生活及社会交往状况等诸多方面,对张栻波澜壮阔的一生做了立体、全景式考察,以更为完整的研究维度逼近历史之真,开拓了教育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范式。107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并创办了城南书院。他以书院为基地,教授与传播理学思想,因此书院教育亦是张栻教育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刘刚认为张栻力推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以外,另一层意义在于抗衡与回应泛滥于当时社会的佛老二氏之学、王安石新学及当时争驰于功利之末的世俗之学。张栻从通经明理、修身成德、经世致用为旨归的理学立场,将佛老二氏之学、王安石新学与重利忘义的世俗治学之风,在不同程度上皆视为“俗学”;并从人性论、心性论语知行观理论出发,对当时“俗学”进行强烈批评与坚决抵制,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反俗学思想。[108]
七、回顾与展望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栻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从思想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研究的视角等方面,皆有进步和深入的空间。笔者认为,今后张栻思想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第一,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勘误方面。资料的完整、翔实与真实,是我们展开研究的基础。首先针对张栻的文集来说,现在仍有许多逸文,比如据苏费翔推测,至少在《朱子语类》、蔡节《论语集说》以及《西山读书记·乙部》等书中还有不少逸文可寻。[109]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逸文,完善张栻的研究材料,一直是我们需要努力之地。另外就文集而言,张栻著作流传版本众多,文字上多有存在差异的地方,易造成解读上的差异。因此对张栻著作进行翔实校勘,整理出一个最能真实反映出张栻思想的版本,很有必要。
第二,关于张栻生平和影响的研究。张栻的年谱可进一步考证、完善和编年,虽然现存有三部张栻年谱,但总体而言,都极为简略,多语焉不详。在现代学者对张栻材料进行了进一步整理和考证后,如书信编年,诗歌编年和涉及人物考证等,可尝试重新编写张栻年谱,进行《张栻年谱长编》,以期能更详尽地展示张栻的生平事迹,并展现其时代的特点、家族系谱、交友状况以及学术思想变化等。其次,张栻思想对海外思想家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张栻交游情况研究。《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信汇编》一书的出版,对于学者研究张栻与同时代的学者交游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有待学者进一步挖掘张栻书信交往中的思想和观点。张栻与其他学者或其他学派,比如与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人之间互动,对蜀学、闽学的影响等,皆可进一步展开。虽然目前对张栻交游的研究,多集中于张栻与朱熹之间,但两者间的学术论辩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就整体性研究而言,目前仍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张栻与朱熹学术论辩方面的专著。另外从研究角度来说,目前对张栻的相关研究,多半集中在张、朱之间对于几个重要理学议题的讨论上,比如中和之说、胡子知言疑义、仁说以及太极说等。这些议题虽在现代学者的努力下,多有成果,但却往往是从朱熹的角度切入,反观就张栻来谈张栻,站在张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朱子之学,对比之下少之又少。换个角度出发,从另外一个视野审视朱子与张栻的交游,一定会有不同于现在研究的新收获。从二者研究的切入点来说,以往大多以中和、仁说等理学命题讨论的形式来展开,然而经典是思想诠释的基础,从具体的经典与经典之间的比较出发,对南轩与朱子的经典著作的诠释风格,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等方面的异同,通过这种比较,如何正确定位二人之间的关系等,皆是我们可以努力展开的研究方向。
第四,张栻思想的重新诠释。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物思想的诠释,亦应与时俱进。有关张栻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距今已过去20多年,这20多年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视野以及研究材料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在新视野、新方法以及新材料的支撑下,充分吸取海内外先进研究成果,深入其义理系统内部,展开深入的、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讨,由此对张栻思想重新进行诠释,是时代对我们发出的要求。其次,抛开哲学思想之外,将张栻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结合起来,从他的心路历程来全新看待张栻变化与发展的一生,给予他全新的定位,也是很有必要的,据此编写类似于《张栻传》等相关的传记,使张栻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张栻研究朝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杨得煜
笔者从台湾2017年度的期刊论文当中,分别摘录数篇来进行说明[1],所摘录论文以台湾重要期刊、重要学者或对朱子义理有新意之学者为主要依据。所选择的论文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第二,韩国朱子学。第三,比较哲学。
为了让读者快速掌握到这些学者之研究成果,笔者以论文问题意识、论文架构、论文摘要等三大项之方式作为架构。这样的架构分类可以帮助读者清楚掌握到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成的程序与结论。
一、宋明理学当代诠释(心性论与工夫论)
1.陈佳铭:《朱子的“心中之理”之研究》,《中正汉学研究》29期(2017年第6期),第1~32页。
(1)问题意识
作者欲以新的观点来重新检视朱子哲学,特别是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朱子心与理之关系,在当代朱子学研究当中,牟宗三先生主张朱子言“心”是气心,心是认知地摄具理,并非是“本具”此理,故其道德实践属于“他律道德”,而不合于传统儒家的成德之教。另一位当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虽然不主张朱子属于“心即理”型态,但强调朱子系统可从“心理相合”“心理一体”,来彰显“理本在内心”之义。杨祖汉教授,则从朱子的“持敬”思想进行研究,认为朱子虽然不能肯定“心即理”,但仍然可以说“理不在心外”,进一步证成此内在于心的道德之理,也可以于心中产生动力,使此理于吾心时时产生作用,故不能说朱子不合于传统儒家成德之教。陈佳铭教授此篇论文即是基于唐君毅先生与杨祖汉教授的观点,进一步阐发朱子心与理之关系。
(2)论文架构
论文章节安排为:第一节,朱子文献中类似“本心”的概念之疏解。第二节,朱子的“心与理一”之义。第三节,格物与心中本有之理。第四节,朱子成德工夫的界限。
(3)论文摘要
首先,在现有朱子文献当中,有类似于“本心”“良知”等概念的出现,认为从这些文献的考察当中,虽然不能将朱子判定为“心即理”的型态,但是也绝不能以“心与理为二”或“他律”来规定。再者,作者进一步透过朱子批评佛教“以心求心”的工夫论,来证成朱子并非是“心即理”型态。朱子认为佛教工夫论,将主体的心另视为一客体加以观之,成了“此心之外,复有一心”的问题。佛教“明心见性”的主张,即是将“本心”当作一对象加以把握,而陷于“以心求心”的困境。而在朱子的观点中,佛教“明心见性”的主张,无异于陆、王的“逆觉体证”模式。
作者认为,朱子心与理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是“心即理”,但是可以说“心与理一”。“心与理一”具有两种意义:第一,“心本具理”。此说明了心“本具”道德之理,而此理也是“已知之理”“本有之知”。第二,理在心中发动。此说明了性理能在心气中发动。从这样的关系中来看,朱子的格致工夫意涵即是指:显发心中本有的道德之理,从自心去体认道德法则,此性理具有某种道德动力。而格物工夫也只是去体证那个“已知之理”,此“理”并非是“心外之理”。
最后,提出三个结论:第一,朱子心性论,虽然不是陆、王“心即理”的型态,但也并不能以“认知心”去理解,而是介于“心即理”与“心具理”之中间型态。第二,朱子格物型态是属于使吾心本知之理彰显、扩充出来。“格物”实为是唤醒、体证本有之理、本有之知而已。第三,此“心本具理”是一种理在气中发的意涵,此理亦可以作为道德动力之来源。
2.陈政扬:《戴君仁与唐君毅论朱子阳明格致思想异同》,《当代儒学研究》22期(2017年第6期),第39~41、43页。
(1)问题意识
戴君仁先生在《朱子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和他们整个思想的关系》一文中,表明此论文与唐君毅先生的观点可以有相互发明之处。但是,作者认为,在此之后,唐先生又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重新借梳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辨析朱子、阳明在宋明理学的思想定位。此时唐君毅先生已经有新的哲学思想发展。作者指出:第一,戴文中仅征引了唐文的结论,而未进一步勾勒出唐文汇出结论的论述轮廓。第二,戴先生作此文时,仅见唐文对朱子阳明“格致”思想的辨析,从而有必要重新考察戴君仁与唐君毅两位先生的论点。可从三个观点来审视此一问题:第一,研究方法的反思。第二,辨析道德理论之有效性。第三,反思儒学本质。
(2)论文架构
论文架构上共有四项环节:首先,先扼要地勾勒戴先生对阳明格物致知说之省察。第二,探究戴文如何辨析阳明评朱子象山说格物之失。第三,以戴先生的论点为主轴,由此对照唐先生的论点,并对比唐戴二先生论阳明格物致知说之异同。最后,在前述三点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反思戴、唐在所见略同处的儒学意义。
(3)论文摘要
作者将戴、唐二先生对于朱子、阳明解析《大学》“格物致知”思想比较出下列几点。在共通方面:第一,在解经方面,两位先生都认为朱子与阳明的诠释并不合于《大学》本意。第二,就儒学发展方面,两位先生都打破了程朱、陆王壁垒分明的对立格局。第三,就《大学》格致思想方面,两位先生皆认为朱子与阳明均是从“道德上”,而非“认知上”阐发《大学》的格致思想。
在不共方面:第一,对于阳明是否可以归属于唯心?两者见解不同。戴君仁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一切事变都是统摄于心体流行当中。唐君毅则认为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并非是朱子、阳明哲学的根本相异处。第二,对于阳明与庄子言“心”,两者见解不同。戴君仁认为庄子的“濠梁之上得知鱼乐”,可以用来解释阳明的“心外无物”。唐君毅先生则是采取儒、道二家理论本质的不可化约性的立场,认为庄子言心是“观照心”;儒家言心是“德性心”。两者在本质上有所差异,不可化约为同一。
二、韩国朱子学
李海任:《韩元震对朝鲜朱子学未发论诠释之省察》,《哲学与文化》44卷10期(2017年第10期),第163~178页。
(1)问题意识
在当前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韩元震(1682~1751)的未发理论,是对于朱熹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朱子哲学中,“未发之中”与“气禀”,此两者是不同的本质。“未发”是至善之“形上学”本体;而“气禀”是属于“形下”领域。作者对于韩元震是否继承了朱子哲学提出了质疑,欲指出韩元震在“未发之气禀”概念上,不同于朱子型态。
(2)论文架构
论文的讨论程序为:第一,可否如既有研究所主张的那样,将韩元震的“湛然虚明”规定为善的反应之根据?第二,若“湛然虚明”并非善的反应之根据,“湛然虚明”是否与“气禀”在本质上相异?第三,若“湛然虚明”与“气禀”皆非善的反应之根据,则韩元震之哲学将如何确保道德性之成立?最后,考察韩元震的“未发论”是否为对于朱熹哲学之继承与发展?
(3)论文摘要
首先考察了朱熹对于“思虑未萌”与“知觉不昧”的理解,认为朱子所讲的“未发”之“思虑未萌”与“知觉不昧”,并非意指意识的状态或流动,而是意指作为“道德性”反应之根据的“心”,此心贯通并主宰形上、形下。如此,韩元震的理论体系中,对于“未发”的定义与朱子的理解不同。“未发”更能对应“知觉作用”,而不是“道德本性”。
第二,考察“未发”问题。在韩元震的理论体系中,“气质之性”并非“未发以后”之物,而是“未发”,亦即与对象接触以前之理与气相结合的状态。
第三,“未发之心”与“气禀”的问题。韩元震并未如同朱子一样,将“未发气象”直接与“理之正明”相连接。理由在于,韩元震认为“未发之心”中,亦存在气禀。在韩元震的理论中,“心”与“气禀”在本质上是“同一”,即皆是气。
第四,圣人与凡人之“虚灵知觉”的问题。韩元震主张“圣凡心不同论”。对于韩元震而言,无论圣、凡,其“虚灵知觉”都是对外物刺激之反应的基底。差别在于:圣人之心“依理”做出反应,而凡人之心“依欲”做出反应。并且圣人之“虚灵知觉”在不同情况下,都具有能发现“法则”的洞察力。
最后,作者指出,对于韩元震而言,“未发之心”并非是道德反应之根据,而是应对外物刺激的心之“知觉作用”;人之道德性反应是建立在道德规范上(性理)。未发之本质是“知觉”,并不异于欲望;而并非如朱熹所主张的那样,是形而上的道德反应之根据。
三、比较哲学
1.陈文祥:《洞察与豁然贯通:郎尼根与朱熹论认知之心及其本性》,《哲学与文化》44卷3期(2017年第3期),第155~172页。
(1)问题意识
在当代认识论中,郎尼根提出了一套认知理论模式,让人可以从体认个别存有到存有本身。另一方面,在中国,宋明理学家之一朱熹,则发展出一套格物致知理论。这两者在认知论中具有相类的论说内涵,特别是在“洞察”与“豁然贯通”这两个主要观点上。
(2)论文架构
分四节进行讨论:第一,辨析二者理论的特征及其侧重;第二,析论郎尼根对主客认识与洞察的观点;第三,朱子讨论格物与豁然贯通的论点;最后则为讨论二者的歧异并做出结论。
(3)论文摘要
首先说明了郎尼根的“异质同形论”。从具体的认知事例中体察“洞察”的实存正是郎尼根哲学起点。所谓“洞察”观念最简单明显的定义就是“瞭悟的行为”(an act of understanding)。然而,如何定义“瞭悟的行为”?作者根据当代学者W.A.Stewart的说法:“理解的活动本身无法定义,因为理解是一种动态的活动。”郎尼根企图推论,透过洞察能力的中介,我们的认识与外在事物的关系是确实的。也就是说:第一,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进行认知活动。第二,我们也肯定了外在物的存在。如此使得认知上的怀疑论是站不住脚的。关键在于:我的认识能力与外在的被认识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相应性”,郎尼根称为“异质同形”(isomorphism)。作者指出,“异质同形”的理论与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具有相互参照的可能性。
第二,朱子言“类推”概念似乎可以和郎尼根所言之“重点不在于认识一切,而在认知者本身的体认”相呼应。从当代思绪理解朱子的认识论,则和郎尼根的“洞察论”几无分别。但是,两者并非没有存在歧异性,朱子与郎尼根的歧异在于“知识本源与根本方法”上。朱子采取的是本体论式之“内在超越”的路径;而郎尼根则是基于传统基督宗教哲学之“外在超越”的路径。
第三,郎尼根“洞察论”,其结论是洞察到唯一的创造者正是人类洞察的顶点;而朱子的“豁然贯通论”,则企图找到万物根本的理,并在伦理生活中体现此理的实存。
2.廖育正:《朱子心性论可以响应道德责任归属吗?》,《台湾大学哲学论评》53期(2017年第3期),第109~143页。
(1)问题意识
当代哲学讨论道德责任归属时,一种常被接受的观点是:“某人对某行为具有道德责任,且为某人在自由意志下,促使了某行为的发生。”若是人无从避免去执行一件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则人不应该被归属道德责任。所以,朱子心性论是否可以响应道德归属的问题?
(2)论文架构
分为五个重点章节:第一到第四节:当代学者所采取的观点。第五节:作者提出学界观点分歧理由以及方法的反思。
(3)论文摘要
如果要在朱子理气二分的义理中,讨论道德责任归属之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聚焦在朱子心性论上的诠释,才可以厘清朱子是否可以响应道德责任归属之问题。再者,对于朱子心性论观点,作者考察了当代学界的研究成果,分类成四种型态,即三种进路与一种批评。第一种进路:心属于气,无以归属道德责任。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第二种进路:心属气,可以归属道德责任。以傅武光教授为代表。第三种进路:心不能说属气,道德责任之归属无理论困难。以陈来教授为代表。最后,一种批评:“道德责任”之相关探讨不完全适用于朱子义理。以祝平次教授为代表。
“朱子是否可以响应道德责任归属?”之问题,其实是“兼容论”与“不相容论”之争的中国式案例。若“心属于气,且可以归属于道德责任”,则属于“兼容论”。反之,若“心属于气,不能归属道德责任”,则合于“不兼容论”者的思维模式。朱子的思想重心不在于保障一个先验的自由意志。而朱子深刻地洞察到“心”作为连接人与理的枢纽,知觉形上至善的天理,同时也具有形下的气禀。作者认为朱子并没有采取过康德式的预设自由意志之进路。对于朱子而言,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应该诘难的问题。要如何理解,作为朱子义理枢纽的“心”?除了从存有进路的探究,仍需并陈以工夫体验——以本体工夫论兼及体验论的视野,去照应涵养省察、格物致知、持敬、克己、致中和等思想概念丛,或许才更能厘清朱子哲学的眉目。
3.苏费翔:《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郑玄与朱熹对“慎独”的解说及西方学者的诠释》,《师大学报》62卷2期(2017年第9期),第111~125页。
(1)问题意识
“慎独”概念在传统中国思想中非常普遍,中国历代学者在这个概念上都下了诸多工夫来解释。慎独的概念同样被20世纪中外学者所重视,而出现诸多的西方翻译。翻译文本在跨文化哲学的脉络中,会对原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论文架构
论文先介绍先秦及汉代的主要相关经典。第二,从语法的角度谈论君子慎独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第三,分析郑玄和朱熹对于慎独的理解。第四,讨论东西学者欧语著作的基本立场。
(3)论文摘要
《中庸》“慎独”思想在当代学者的诠释下,其哲学含意有两个层面:一方面言人人必谨慎小心,属于修身工夫(此为学者比较重视的一点);另一方面又谈论所“显见”的“隐微”之物,并与“道”相连“所不睹、不闻”之事,涉及“知识论”领域。
“慎独”有两种角度。在《中庸》中的第一段(作者称之为A):“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段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其所不睹、不闻”指“君子被他人所不睹不闻”(作者称之为A1);其二,“其所不睹、不闻”有可能指“君子自己不睹不闻”的事。(作者称之为A2)
在《中庸》中的第二段(作者称之为B):“君子慎其独”。此段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可指“君子独居”,即“他人看不到君子”的场合(作者称之为B1)。其二,“独”又可指“君子独知”,即“只有被君子所感到”之事(作者称之为B2)。
从思想意义的角度来看:第一,【A1】与【B1】两段和“不愧屋漏”的意思很相似。第二,【A2】言“君子所不知”之事,代表最奥妙的一层面;不但隐含着任何人不睹、不闻的地方,而又可以引申无法用逻辑思想的方法来推断之事。此是谨慎恐惧到最高极限。
在郑玄与朱熹注疏方面,在郑玄《十三经注疏》中,【A】段与【B】段,都是采取“不愧屋漏”的概念,即【A1】与【B1】的解释。而在朱熹《中庸或问》中,于【A】段中,很明显的是用采取【A2】的立场。但是在【B】段中,朱熹同时采用了【B1】与【B2】的解释。
在西方学术界中,陈荣捷与杜维明的英译,两人同样都采取了【A2】与【B1】的解释。作者指出,卫方济的解释很类似朱熹,理由在于:“耶稣会传教士在解读《中庸》经文时与中国官方的学者合作,故选用以朱熹为主的解说。”当代德国汉学家鲍吾冈(Wolfgang Bauer,1930~1997),在《中庸》【A】段中,采取了【A1】的解释;在【B】段中,则采取了【B1】的解释。作者引鲍吾冈的观点,认为在【A】段中,【A1】是中国早期思想家的见解,而后来心学派将此段误释为【A2】。
当代的英译本中,对于【A】段与【B】段的解释则都采取了理雅各布的解释,即【A1】与【B1】的解释。理雅各布塑造了一个说法,影响了后来的翻译者。相较于中文,印欧语系的语言比较明确地表达动词的主动式与被动式,因而这些西方译著往往会缩小经书原文广泛的含义。作者认为翻译在跨文化哲学的脉络中会约束原文的含义。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
2017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
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韩﹞姜真硕
2017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朱子学研究、退溪学及韩国儒学研究、茶山学研究、韩国儒学的其他论辩以及东亚儒学研究等五个领域。
一、在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方面
学者们提出朱子的忠恕论、心理治疗、太极解义论、主敬论、修养论、仁说以及朱子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等主题研究。主要的论文有《朱子的欲望观及其现代意义》(Jeong Sang-bong,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文化研究》67卷,2017);《朱子道德论中的敬的地位和意义及其来源的研究》(Hwang Gab-yeon,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40卷,2017);《朱子<太极解义>一考:以其世界观为主》(Sho Hyon-seong,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39卷,2017);《关于张栻“仁”的小考》(Lee Yun-jeong,韩国哲学史研究会,《韩国哲学论集》55卷,2017);《朱子哲学的忠恕概念分析及其伦理学的含义》(Kim Hye-su,韩国中国学会,《中国学报》80卷,2017);《哲学治疗与朱熹的修养论:以心概念和涵养为主》(Ahn Jae-ho,中央大学中央哲学研究所,《哲学探求》47卷,2017);《朱熹<武夷櫂歌>与朝鲜道学者的反应》(Kim Tae-wan,崇实大学韩国文学科艺术研究所,《韩国文学与艺术》24卷,2017);《关于<周易元亨利贞的解释的比较研究:王弼、程颐、朱熹、丁若镛》(Seo Gunsik,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精神文化研究》40卷,2017);《絮矩之道与公正的主体之条件:以朱子与茶山为主》(Hong Seong-min,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41卷,2017);《朱子忠恕论的多层解释的探讨》(Kang Jin-seok,朝鲜大学人文学研究所,《人文学研究》53卷,2017)等。
1.金惠洙:《朱子哲学的忠恕概念分析及其伦理学的含义》
金教授说明“忠恕”是一个道德实践的伦理原则,是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两种原则。在中国方面,冯友兰和劳思光先生已经详细探讨过这些内容。他们主张“忠”为积极意义的伦理原则,恕为消极意义的伦理原则。就韩国学者的研究而言,他们一方面主张儒家的忠恕大体上不异于西方基督教的“你们希望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等黄金律思想,但另一方面把儒学的“恕”看作否定意义的黄金律,而且从道德义务论的角度去回应康德批判黄金律的内容。金教授介绍在朱子忠恕论中,“忠”为被作为道德本体的天道的实现,“恕”为实现公正对待的伦理原则的作用即人道。因此万事万物的“恕”是由“忠”所贯通的。金教授认为朱熹的“忠”具有义务论的伦理意义,就是说“忠”表示应当实践的道德法则,是把“理”作为“尽己”的义务来实践的。从此进一步说“忠”就是尽己之道德原理的道德意志,不仅可创造出许多的道德规则,而且通过“恕”可展开具体的实践方向。“恕”为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伦理。这是朱子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解释。
金教授又认为朱熹把“恕”的禁止给予他者损害的道德行为作为标准,这与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说的“禁止损害的原则(no harm principle)”大同小异。这种“禁止损害(no harm)”行为就是为走进最低要求的道德社会所需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也是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当今韩国社会需要的一个原则。朱子除了“推己及人”以外,还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表示人们如果要做自己的道德实践,则要把遵循内在于自我的道德法则的道德义务,积极实践于他者身上。从忠恕的角度看,“仁”是指自律的道德义务,就是主动为他人做善行及奉献的义务。这种积极意义的义务就超越应当或应该遵守的道德义务的范围,成为博施于群众之爱的道德原理。这可与道德义务的“忠”相通,也可与“推己及人”之“恕”的具体运用相应。朱子相信如果每人实践“推己及人”和“以己及人”等伦理原则,则可以实现成熟的伦理国家。
2.洪性敏:《絜矩之道与公正的主体之条件:以朱子与茶山为主》
该论文是关于朱子与茶山絜矩之道的比较研究。洪教授掌握了朝鲜时代韩国儒者对絜矩之道论辩的大量资料,因此注意到了絜矩之道具有的几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政治家不具有公正的准则即“矩”,那么就在“絜”即观察百姓的生活条件方面会产生差错,也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此絜矩之道正是政治家对待百姓时所需要的公正的态度。朱熹主张,进行“絜矩”之前,先需要道德主体的修养,要确立既普遍妥当又公正的道德主体。此修养的方法有致知、诚意正心等。格物致知是用来要把握他者之心,也是认知主体与他者间具有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由此可确认我(道德主体)的心正如他们的心。诚意正心则是指道德主体省察私欲和自我中心倾向,而后可得无私之心。洪教授认为朱子絜矩之道和恕不仅表示两人或三人在日常关系中单纯地交换立场而思考的道理,而是表示一个主体先把握公正性和道德性,然后依此来公正地对待他者的原理。一个道德主体要先确立道德性,才能公正地对待及忖度他者。由此可看,在朱子的道德实践思想中,絜矩之道及恕本身不具有一个独立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是从道德主体之树立后才能发生的一种结果。在朱熹看来,自我与他者互相交换立场或是同等对待等的逻辑概念会带来两者本身具有的恶也可被容许的一种诡辩。恶人宽恕另一恶人,互相承认对方的错是在同质化的逻辑上可被接受的。如果因为有恕的伦理会发生主体与他者互相容忍的恶,恕就不能成为一生可遵循的伦理准则。
相对的,洪教授认为茶山丁若镛的恕是指对待他者时尽己的忠实。换言之,如果没有人跟人之间的交际,就根本不存在可尽忠实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茶山说恕是根本,忠是其实践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完备一贯之道。茶山认为,《大学》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原本是语序导致的,因此我们应当念出原来的含义即“求诸人而后有诸己,非诸人而后无诸己”。这里的恕不是主体道德性的扩张,而是自我修养的方法,也是工夫的开始。我们通过恕的态度可反省自己也需要改正修养。就是说把对他者的要求找回于自己身上,把它作为自我修养的课题,这才是“恕”的修养方法。父子关系、上下关系不外如此。互相交换立场,以他者的视角反省自己,消除私心,然后一个主体才能树立公正的态度,也公正地对待他者。洪教授认为,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对他者的要求和从他者所忖度而来的情感是本人自己要实行的道德义务,在与他者交际中反省自己,要确认自己的伦理道德,就是树立公正的自我即“矩”的具体方法。此种方法是在现存的人际关系网中才能施行的,与朱子的伦理方式相差很远。
3.姜真硕:《朱子忠恕论的多层解释的探讨》
该文首先介绍孔子忠恕论与世界宗教的黄金律思想的比较。不管是犹太教、伊斯兰教或是印度教都有着与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类似的伦理思想。到了朱子,孔子的一贯之道变成忠恕体用的形而上学,即“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本体之忠根据于天道的原理,而作用之恕是本体之于现实世界的分化过程。该文介绍以往不少的韩国学者从道德义务或是道德责任的视角探讨过朱子的忠恕思想,这主要是针对康德的黄金律批判而回应的。但笔者对这些看法提出一些质疑。就是说朱子哲学不仅讲到圣人之道或是如何成为圣人的圣学工夫,并且很重视学人及凡人之道即困而知之、学而知之等修养工夫。朱熹的忠恕论也不例外,是说朱熹说的“恕”的确是包含着多层解释的话语。如果从道德义务的角度论到忠恕思想,就会局限于圣人之忠恕论题,然而在学人及凡人的忠恕,则却还需要许多的修养工夫的过程如穷理、正心等。因此拙文认为,我们要把焦点从忠恕有否道德义务的根据或是道德标准是否准确的论点,移动到孔子本来要说的是什么或是朱子原来要说明的要旨在何等主题上。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通过穷理和正心的工夫要学习及认知道德标准,由此要进行调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知和调整的过程不是被激发于道德主体自律及主动的实践一面,而是产生于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标准与忖度及反求自己不愿与不欲的侧面。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个方面。
学人的道德标准不像圣人那样生而知之的,他们不管在认识道德标准或是实践伦理原则上,都需要不断认知它的修养过程。凡人在以道德原理来判断好恶、是非的能力上都有困而知之之处。格物穷理就是对这些人最要紧的修养工夫。朱子讲到絜矩之道时,特别强调此格物穷理的工夫。道德标准不是先验地赋予我们,而是通过穷理和正心工夫后才能得到的。因此我们讲道德义务前,应该先弄清自我的道德标准,然后可把它努力做实践。凡人的“反求诸身”不仅表示一种调整自我道德标准的行为,同时也是与他者共同进行道德关系上的协调的过程。另一方面,朱子从自然与人为的角度讲过仁与恕的区别。自然的行为与人为的努力的区分反映着自律和主动地实践与需要修养和调整的实践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仁与恕的区分不是说明积极与消极或是肯定说法与否定说法的差异,而是要说明不同层次的工夫及概念。这里说的忠恕是学人和凡人层次的行为者不断寻求及探索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一个过程,也是认知自己的道德标准后把它适用于他人身上而寻找相互协调的过程,又是在此过程中把自己的道德原则强恕而行的实践行为。拙文又介绍朱子说的“三摺说”。朱熹把絜矩之道看作一种三摺之册,就是说絜矩之道不是一对一的个人伦理,而是三人以上的共同体伦理。王庆杰(Wang Qingjie)等学者把它称为共同体化。朱熹说过絜矩是在人际网络上要确认自己的本分和范围,各自重新调整自己的中心后,得出既协调又中节的共同体伦理的过程。互相共同体化的伦理倾向拒绝先验地被赋予个体的一种绝对律令或是道德义务。追求共同体化的儒家伦理不是要绝对化而是要实例化,也不是要命令化而是要协议化,又不是要规律化而是要持续教化。
上述的三篇论文,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朱子忠恕与絜矩之道,反映着当今韩国学者对朱子的伦理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4.黄甲渊:《朱子道德论中的敬的地位和意义及其来源的研究》
黄教授介绍以往当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等都主张朱子的敬思想是一个不完整的后天的他律工夫。但黄教授本人对这些看法提出一些疑问,由此就梳理了朱熹敬思想的各种内涵。该论文说明在朱子哲学里敬与虚静的关系不是说以敬为主要工夫而以虚静为附属工夫,而是虚静是个敬工夫的附属效果而已。因此在敬工夫中虚静不是个排斥的对象,也不是可代替敬的另一工夫。在朱子道德论中,敬是个能够恢复心之湛然虚明作用的工夫,这不是一种静态的工夫,倒是一种使得心之思虑作用从而完善地发现的动态工夫。黄教授介绍,朱熹的敬工夫如果一直强调整齐严肃等外向工夫就有陷入形式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必须与收敛、常惺惺、主一等内向工夫并行。无妄思是属于收敛、常惺惺、主一等工夫,无妄动是整齐严肃等外向工夫。朱子通过敬工夫完成了内外兼修的工夫。
黄教授认为,朱子说的主一和常惺惺工夫都照理作为自己的内涵。这是儒家和佛教的差异。虽然在朱子心性论中,心与理在概念和本体论上是显示二元形式,但心对理有无条件的尊敬和喜悦,理亦是以自身的法则性和至善性不断引导心。朱子说的敬是在心与理的合一状态中发挥其作用。黄教授认为敬工夫不是从心之外在到来的工夫,而是心之自觉本身。朱子的道德论不像牟宗三先生说的他律工夫,而是属于自律道德论系统的工夫论。心统性情也是由敬工夫所决定的。敬是贯通于内外、有事无事、动静的工夫,是贯串于道德的全范围、心活动的全领域的全面工夫。那么,牟宗三先生特别低估朱子敬工夫的那些误解何来?第一原因可能是朱子特别强调整齐严肃等外向工夫。第二是牟先生把朱子哲学中的性理与心的关系过度地看成认知上的摄具,因而排除了心之对性理的自发、自愿的喜悦和尊敬的内容。
笔者认为黄教授以细密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朱熹敬工夫具有的多层含义,尤其是从客观的态度重新论证了当代新儒家对朱子学的看法。
二、在退溪学与韩国儒学方面
韩国学者研究《心经》的解释、《大学讲义》的比较、哲学的比喻和象征、杨村权近的思想、霞谷的《中庸》解释、退溪的敬思想及活人心方研究以及四端七情论辩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朝鲜儒者对心修养的省察——国译<心经>注解总览》(Han Geong-gil,历史实学会,《历史实学》62卷,2017);《16世纪后期朝鲜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学论争——以<大学讲语>的经学论争为主》,(Lee Hyung-sung,韩国思想文化学会,《韩国思想与文化》88卷,2017);《哲学的比喻和象征——17世纪朝鲜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与统摄的世界观研究》(Kim Seung-young,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39卷,2017);《霞谷以朱王二元结构解释<中庸>》(Hwang Yin-ok,凡韩者学会,《凡韩哲学》86卷,2017);《时代<明儒学案>的读解情况及其性格》(Kang Gyong-hyeon,韩国阳明学会,《阳明学》46卷,2017);《初期退溪学派门人对<心经附注>的理解和退溪学的心学倾向》(Lee Sang-ho,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34卷,2017);《从退溪与杨明的修养论的比较研究考察朝鲜时代阳明学未扩散的原因》(Kang Bo-seng,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文化研究》68卷,2017);《退溪李滉的<活人心方>与诗形象化》(Xia chung-won,韩国文化融合学会,《文化与融合》39卷,2017)等。
1.金昇泳:《哲学的比喻和象征——17世纪朝鲜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与统摄的世界观研究》(《儒学研究》39卷,2017)
金教授收集大量的文献,从而介绍了17世纪韩国儒者所使用的许多比喻和象征的内容。他涉及的文献内容十分广泛,因此他的论文值得参考及引用。他介绍退溪学派的儒者活斋李榘(1613~1654)。李榘活动时期正好是李栗谷的学说逐渐扩散的时期,此时他用几个比喻来辩护退溪哲学的宗旨。他说“愚谓理犹柂也,气犹船也,心犹人也。非船则柂无所掛撘,非柂则船不能运行。主之者乃人。有时柂动而船随以行,有时船发而柂乘以运。人或任船而行,不无胥溺之患,必用柂以运自有利涉之道也。”(《活斋集》卷三)由此李榘强化了退溪哲学的理气互发说。沙溪金长生(1548~1631)用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格物说。他提出格物的比喻,支持李栗谷的格物论而批判郑经世(1563~1632)的“请客而客来”(这里请客指格物,客来指物格)的看法。金长生说“譬如暗室中,册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而缘黑暗不能见物,不可谓之册衣箱在其处也。及人灯以照之,则方见册衣箱各在其处分明,然后乃可谓之册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极处,非待人格之而后始到极处也。只是人之知黑暗未能见理,则岂可谓之理到极处耶。理非自解到极处,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到未到也。”(《沙溪遗稿》卷四)
愚潭丁时翰(1625~1702)用月光的比喻说明理与物的关系。他说“天上之月光,虽不以物之清浊虚实,照有不遍,而浊实之中既不见月之光影,则不可谓浊实之中月光之本体存焉。若以隐于无形,谓浊实之中月光之本体存焉,则是求理于悬空,无用之地,而其所谓本体之明于何见得乎。”(《愚潭集》卷四)尤菴宋时烈(1607~1689)用器与水的比喻来说明心性情的关系。他说“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中泻出者也。只言虚灵而不言性情,则是无水之空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虚灵,则是水无盛贮之处也。是三者缺一,则终成义理不得,岂得谓之明德乎。盖或者之意以所谓虚灵不昧者为释明德之意,故有此说。而不知所谓明德者是心性情之总名也。”(《宋子大全》卷一〇四)明斋尹拯(1629~1714)用行路的比喻说明“格物”与“物格”的差异。他说“今以行路言之,行路格物也,路尽物格也。欲至某处者致知也,既至某处者知至也。今曰人欲至某处则当行路,路既尽则已至某处矣。如此看,岂非晓然耶。然则,欲至某处既至某处者,主人而言也。”(《明斋遗稿》补遗)
笔者认为金昇泳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朝鲜时期韩国儒者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和象征比喻方面的许多资料。如上介绍的“理犹柂也,气犹船也”“请客而客来”“人灯以照之”“天上之月光”“器与水的比喻”“行路的比喻”等话语不仅丰富了朝鲜时期韩儒的思维方式,也显示了他们对朱子学的理解内容。
2.姜卿显:《朝鲜时代<明儒学案>的读解情况及其性格》(《阳明学》46卷,2017)
该论文提供朝鲜时代的韩儒如何运动及理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文献的事实。照姜教授的研究,当时读解《明儒学案》的韩国文献有《青庄馆全书》(19世纪初)、《研经斋全集》(19世纪中期)、《五洲衍文长笺散稿》(19世纪中期)等。这些文献都是属于明代人物及思想的一种资料集。因此可知,当时这些文献的作者都把《明儒学案》看作一种可参考的资料文献,他们把《明儒学案》运用为可参考明代人物的行迹和言说的一种传记类的文献。他们不太重视《明儒学案》由黄宗羲的视角所编撰的事实,只是用来收集有关明代人物的史料。
当时韩儒李圭景正视了在《明儒学案》中列举的人物包括朱子学和阳明学等各种学派。他不因其书倾斜于阳明学而排斥它,而是从圣门的宏观角度容纳它。姜教授认为李圭景一类的看法反映着当时学者把《明儒学案》看成明代各种学派的思潮史料,以此可参考朱子学和阳明学等思想。相对的,当时李裕元一类的学者从朱子学的角度批判地看待《明儒学案》。他说“盖其书两学俱载,其言论义理,如镜照而烛行,自可发明。余钞作一书,编于笔记之末,俾自解其正邪之别云。”(《林下笔记》卷7)这两种类型的学者们对阳明学都有一定的批判的态度,但是他们总算不完全排斥明代盛行的两种学潮的史料事实。但是到了第三类型的学者们,对阳明学的批判相当猛烈。姜教授介绍属于第三类型的韩儒有吴熙常(1763~1833)、洪直弼(1776~1852)、田愚(1841~1922)等人物。特别是吴熙常说明儒除了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以外没有可参考的,认为这三人以外,大部分的学者脱离朱子学各自树立门派,结果都流于禅学。韩国的阳明学派运用《明儒学案》史料的事实,在朝鲜时代中没被考证。到了日本殖民时期,在朴殷植(1859~1925)的《王阳明先生实记》和郑寅普(1893~?)的《阳明学演论》中,可找到被引用的记录。
三、在茶山丁若镛研究方面
有《丁若镛与李震相的公七情说的比较》(Lee jong-woo,《洌上古典研究》56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游览及纪行中凸显的风流及其意义:以记文与纪行诗为主》(Kimjong-ku,韩民族语文学会,《韩民族语文学》76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风水观:批判与继承》(Lee Kong-sik,Chon Yin-ho,釜山大学韩民族文化研究所,《韩国民族文化》64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实践德论的考察》(Oh Soo-lok,韩国儒教学会,《儒教思想文化研究》69卷,2017);《茶山丁若镛的侄女丁兰珠的在济州岛的流放生活与天主教》(Hong Dong-hyon,延世大学茶山实学研究院,《茶山与现代》10卷,2017)等论文。
在此,着重介绍李宗雨教授《丁若镛与李震相的公七情说的比较》一文。李教授介绍韩国儒学的“公七情”说。此公七情学说是韩儒星湖李瀷(1681~1763)在解释李退溪与奇大升的四端七情论辩时所提出的。后来受到李瀷影响的茶山丁若镛(1762~1836)与寒主李震相(1818~1886)对这些学说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李瀷门人针对李瀷的公七情,各自提出公七情理发和公七情气发等不同看法。后来丁若镛受到李瀷的影响主张公七情是从天命而发的,说“凡公喜公怒公忧公惧,其发本乎天命”。但李震相认为公七情是理发的,他说“星湖晚年,亦主公喜怒理发之说”。茶山批判天命之性为理,七情之发为气等说法,也不同意朱熹的性即理等学说。韩国学者对丁若镛的说法议论纷纷,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茶山受到《天主实义》影响的原因。但有些学者主张丁若镛受到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的影响。李教授介绍当今学者李光虎教授主张茶山年轻时在《中庸讲义补》支持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说,但到四十岁以后在《理发气发辩》中受到退溪之理发说树立了上帝说。相对的,李震相主张七情也有理发,但不是每个七情都是理发,而是发而皆中节才有理发的。
四、在韩国儒学的其他论辩研究方面
主要论文有《济州的朝鲜儒者边景鹏的双重文化认同》(Kim Chi-wan,韩国文化融合学会,《文化与融合》39卷,2017);《南堂朴昌和对韩国疆域的论辩和认识》(Park Nam-soo,新罗史学会,《新罗史学报》41卷,2017);《西厓柳成龙的阳明学批判》(Choi Jong-ho,东亚人文学会,《东亚人文学》38卷,2017);《从儒学到汉学:20世纪60年代之后韩国儒教政治运动的衰退过程研究》(Lee Hwang-sik,东洋社会思想学会,《社会思想与文化》20卷,2017);《在近代话语中儒学者李树廷1 885年把<马可福音<翻译成韩语的意义》(Kim Shin,21世纪基督教社会文化学堂,《神学与社会》31卷,2017);《田愚的西学认识及其斥邪论:以<自西徂东辨>和<梁集诸说辨>为主》(Lee chong-lok,朝鲜时代史学会,《朝鲜时代史学报》80卷,2017)等。
金信教授的《在近代话语中儒学者李树廷1 885年把<马可福音>翻译成韩语的意义》一文较为突出。金教授介绍朝鲜后期儒学者李树廷(1842~1886)一生致力于翻译基督教《圣经》的时代意义。李树廷活动于封建朝鲜的没落与近代社会的转变的交叉时期。李树廷一方面坚持朱子学者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回心,从此开始做翻译工作。他的《圣经》翻译是到日本之后正式开始的。当时他把Bridgman与Culbertson翻译的《旧新约圣书》作为原始资料,以及在传教士Henry Loomis(1839~1920)的助力下所成的,然而李树廷始终吸收朱子学的思想资源。金教授简略地介绍韩国的《圣经》翻译史。自从1877年苏格兰传教士John Ross(1842~1915)和李应攒一起把中文《圣经》翻译成韩文《圣经》以来,1878年他们又翻译了《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以及与徐相崙(1848~1926)一起完成了《路克福音》的翻译。1879年John McIntyre和白鸿俊一起翻译了《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以及《罗马书》等。1882年,中国沈阳的文光书院首次出刊了韩文《耶稣圣教路克福音全书》和《耶稣圣教路约翰音全书》。1885年在日本,李树廷出版了《马可福音》的韩文翻译本。李树廷的翻译工作具有先设定读者对象的一个特色。他的翻译是针对当时懂汉字的知识分子而做的。因此与专用韩语来翻译的Ross的翻译不同,他采取汉韩文并用的翻译方式。这种圣经翻译叫作“悬吐圣书”。
笔者认为金教授的论文提供了朝鲜末期朱子学者受基督教影响下分化的一个脉络。这为韩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在东亚儒学研究方面
主要论文有《董仲舒哲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Hong Won-sik,东亚人文学会,《东亚人文学》39卷,2017);《梁启超的格义西方哲学研究》(HwangZhong-won,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儒学研究》42卷,2017);《伊藤仁斋的儒教概念中凸显的古义学体系及其理念——以<论语古义>的概念分析及宋儒批判为主》(Lee In-hwa,韩国东西者学会,《东西哲学研究》85卷,2017);《山鹿素行的<中庸>解释——以与朱子的心性论做比较为主》(Lim Ok-kyun,东洋哲学研究会,《东洋哲学研究》90卷,2017);《山鹿素行的<大学>解释——以与朱子的心性论做比较为主》(Lim Ok-kyun,东洋哲学研究会,《东洋哲学研究》89卷,2017);《近代日本的“修身”理解——以荻生徂徕与山鹿素行的思想为主》(Tokusike Kumi,An Hae-yeon,釜山大学人文学研究所,Cokito82卷,2017)等。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7年度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福谷彬廖明飞译
和2016年一样,2017年度日本学界有关朱子及其后学思想(狭义的“朱 子学”)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扩大了收录范围,介绍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的宋学 研究(广义的“朱子学”)的最新进展。本文分专著、单篇论文依次做介绍,最 后总结本年度的研究并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
ー、专著
1 .下川玲子⑴:《从朱子学中思考的权利的思想》⑵
该书从权利思想的观点出发,重新检讨朱子学在日本的意义,提出朱子学的 尊严论与西洋式权利思想具有亲和性,与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权利思想相似,探 寻如何能够活用权利概念及朱子学的思想。全书目录如下:
Ⅰ朱子学の論理と人権の論理
第1章 西洋の権利の思想
第2章 朱子学の尊厳論
第3章中江兆民における朱子とルソーの受容
第4章 近世儒教を把握する視点
Ⅱ朱子学の現代的諸問題
第1章 寛容論と権利の思想
第2章 武士道の論理と権利の思想
第3章 死刑廃止論と朱子学
第4章福祉国家論と朱子学
该书指出,日本前近代的朱子学,不单是被西洋的近代思想驱逐的旧思想, 在接受西洋的近代思想方面也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的主张,以在日本的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名著——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批 判性的前提。以下,在介绍丸山著作内容的同时,对此主张加以评价。
丸山将荻生徂彿视为日本近世思想成立的划时代的人物,认为被徂彿学否定的朱子学是前近代旧思想的典型。根据丸山,朱子学的“道”并非由人创造,而是天理的自然。与此相对,对荻生徂徕而言,“道”是圣人通过“人为”(“作为”)创造出的制度和文物。依据朱子学的观点来说,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一般想法,本来应该是与“天理的自然”一致的,不应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与此相对,荻生徂徕认为,社会的秩序是统治者通过积极“人为”(“作为”)创造出来的,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必须根据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重新创造出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社会的一般想法。丸山指出,江户时代思想的变化,与西洋从基督教神学的“自然”观念到以托马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人为”(“作为”)思想的变化过程相似。从这一相似变化中丸山探寻“近世”究为何物。如此,丸山描绘的日本近世史观就是朱子学(“自然”的思想)的解体,徂徕学(主体性的“人为”[“作为”]的思想)的勃兴的过程。
下川氏对丸山的批判,其矛头指向的是丸山以霍布斯为到达点的近世史观和对朱子学在近代日本的影响力持否定性理解的态度。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如果没有统治者的管理,民众甚至无法生存,民众必须将“自然权”的一部分委托给统治者。霍布斯肯定民众无法批判君主的绝对王权。下川氏指出,这样的相比民众个人的权利,以政府的意向为优先的观点,是与“近代”背道而驰的。
与此相对,下川氏发现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权”论是近代思想的到达点。洛克论述了为了保卫民众本来的权利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下川氏从这样的尊重人们权利的观点中找寻出“近代”,从这一观点出发思考朱子学。
下川氏着眼的是朱子学的人性论与西洋的人权思想的相似性的观点。朱子学的性善说认为,人无论贵贱,生来即平等地具有绝对善的本性。下川氏指出,“自然权”(natural rights)一语,日语也翻译作“天赋人权”。正如这一语言本身即是以朱子对《中庸》“天命之性”的解释为典据[3],它清楚地表明,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在荻生徂徕是没有的,反而是朱子学的人性观才具有与西洋式的价值观的亲和性。如上,下川氏从多种角度阐述朱子学的价值观和近代性的价值观的相似点。
二、论文
1.中嵨谅[4]:《陆学的“人心”“道心”论——追踪所谓“朱陆折衷”的渊源》[51]
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先行研究认为,以折衷朱子和陆九渊的思想为目标的“朱陆折衷论”,在陆九渊的门人弟子一派中有显著的立场。[6]与此相对,中嵨氏指出,“朱陆折衷”的立场,不仅陆九渊的门人弟子一派,陆九渊自身的思想也已经有此端倪,而且,朱陆学问的决定性的决裂,是由陆九渊的高弟杨简造成的。
中嵨谅特别讨论了围绕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出典的“人心”“道心”的解释。中嵨氏检讨围绕“人心”“道心”的朱子对陆九渊的评价,又通过考察陆九渊及其初传、再传弟子的“人心”“道心”论,阐明了朱陆及其门人弟子如何面对朱陆对立的问题。
首先,作为朱陆议论的前提,有程颐的“人心道心”论。程颐将“人心”理解为“人欲”,“道心”理解为“天理”,截然区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是理应消灭的恶之心,“道心”是理应张扬的善之心。朱子最开始赞同程颐的这一说法,后来改变了立场。[7]1
朱子考虑到如果将“道心”视为天理,“人心”看作“人欲”的话,本来应该是同一之“心”会变成有两个心,所以朱子主张认识到道理时就是“道心”,感觉到声色臭味时就是“人心”。朱子认为,“人心”“道心”称呼的不同,是同一之“心”在面对不同对象之际心起到的作用有不同,因此才有二者的区别。
又,中嶋谅分析关于陆九渊的“人心道心”论。陆九渊的“人心·道心”论的特征是强调“人心”和“道心”的一致。但是,陆九渊并非倡导“人心”具有无条件的善性,而是重视《尚书·多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之语,即使是同一之“心”,也会因其心端正与否,而有“圣”和“狂”之别。因此,朱子解释“人心惟危”,认为是表达了心能够变恶的危险性。
朱子对陆九渊的“人心道心”说给予高度评价,批判程颐的说法。此后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强调“道心”和“人心”的一致,在主张“人心”非恶上与陆九渊之说方向相同。中嶋谅指出,关于“人心”,朱子与陆九渊抱有同样的见解,虽然朱子批判陆九渊迷信心之善性,但如果正确地解读陆九渊的著作,则可知陆九渊并没有朱子所批判的那种主张。
其次,中嵨谅考察杨简(慈湖,1141~1226)的“人心道心”论。中嵨谅通过分析《慈湖遗书》所收《论论语上》《论中庸》《泛论学》的内容,指出杨简将“心”看作完美无缺的善,否定心需要外在的修养。因此,中嶋谅指出,杨简的“人心”论与陆九渊强调心的修养和学问的必要性的“本心”论完全不同,杨简曲解了陆九渊的“本心”论。
最后,中嶋谅进而考察与杨简齐名的陆门高弟袁燮(絜斋,1144~1224)和钱时(融堂)的“人心·道心”论,指出他们的思想与陆九渊相同。
通过以上的考察,中嵨谅得出以下的结论。(1)陆九渊、袁燮、钱时绝非仅强调心的善性,相反,他们倡导学问修养的必要性,而杨简的主张中不能看到这ー倾向。显然杨简的立场在陆学一派中是特异的存在。(2)关于“人心・道心”论,朱子同意陆九渊的见解。在此意义上,陆学本来并没有从正面与朱子的思想相对抗,是杨简造成了陆学与朱学对立的尖锐化。(3)过去杨简被视为陆九渊最有力的继承者。但是,根据中嶋谅的研究可知,在有“甬上四 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之称的陆门高弟中,与师之陆九渊思想立场 最为乖离的即是杨简其人。
2.林文孝⑻:《“仁と為す”抑或“仁を為す”:根据朱熹〈集注〉的〈论 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的训读》[9]
“训读”是将古代汉语的汉字按顺序排列改写翻译成日本古语的传统的解读古代汉语的方法。因此,毋庸赘言,即使关于“训读”的研究作为日本人而言有多重要,作为没有必要使用“训读”的中国人来说,则完全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本文特别要介绍该篇论文,是因为在此篇论文中考察的如何训读 的问题关系到对朱子思想的理解。
林氏的论述举出的问题是:如果根据朱子的注释,《论语•颜渊》“克己复 礼为仁” ー节应该如何训读。此条经文及朱子之注如下:
【经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朱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 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 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 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
根据林氏,日本的论文所见《论语》此条经文“克己复礼为仁”的“为仁”的训读有两种:(1)训读作“仁と為す(看作仁)”[10],(2)训读作“仁を為す(做仁)”[11]。但是,关于《集注》的“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的“为仁”,(1)(2)两种场合都训作“仁を為す”的占了大部分。也就是说,(1 ) 的立场,经文和朱注的“为仁”的训读是不同的。
如上,朱子将“克己复礼”的“克”解释为“胜”,将“己”解释为“身之私欲”,将此条经文解释为是在阐述“灭人欲、存天理”的道理。问题是“克己复礼为仁”的“为仁”的解释。如果训作“仁と為す(看作仁)”,则孔子是说“克己复礼”就是“仁”。与此相对,如果训作“仁を為す(做仁)”,则孔子是说通过“克己复礼”来“实践仁”。这并非仅仅是ー个字的解释的问题,而是关 乎“克己复礼”和“仁”的关系这ー重大的思想问题。
在朱子的注释中,“克己复礼为仁”的注有“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如前(1)(2)的立场关于经文的训读是对立的,关于朱注则都以“仁を為す” 的意义做训读,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问题是关于经文,本来与注ー样应该按照“仁を為す”的意思理解,但《语类》中确实存在说明应当按照“仁と為す”的意思理解的记录。”2]林氏考证这些说法的时期,指出相比按照“仁と為す” 的意思理解的时期,按照“仁を為す”的意思理解的是朱子晚年时的记录。[13]
通过以上的考察,林氏指出,朱子对经文和注的理解都是“仁を為す”的 意思。
最后,林氏还言及“仁を為す”和“仁と為す”的解释不是互不相容的矛 盾。“仁を為す”的实践,指的不是开拓未知的地平的行为,而是回归人的本来 状态的行为。如果保持达到实践“仁を為す”(做仁)时的视点,该行为的主体就在成为“仁”的状态,也即与“仁と為す(看作仁)”一致。也就是说,朱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时的“为仁”,有读为“仁と為す”和读为“仁を為す”两种意义。虽然朱子对此做了大致的区别,但并没有做截然的区分,两种意义有 重合的地方。也正因此,两种解释都能够成立。
3.福谷彬”句:《陈亮的“事功思想”及其孟子解释》[15]
福谷讨论的陈亮(号龙川,1143〜1195)是与朱子有过“义利•王霸”论 争的思想家。
“事功”主义的表述,是朱子批判陈亮的语言。“义利・王霸”之语典出《孟子》,一般来说,相比结果和利益,孟子是更加重视动机和道德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正如陈亮的思想被评价为“事功主义”或“功利主义”ー样,他的思想容易被认为相比动机的善恶更看重功利的大小。因此,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多认为陈亮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是对立的。但是,实际上陈亮从年少到晚年都写过尊崇《孟子》的文章,经常引据《孟子》展开自己的论述,反复申说比“利”更应该重视“义”。福谷留意到陈亮尊崇《孟子》的侧面,从陈亮是如何解释《孟子》这ー角度岀发,试图重新解明陈亮的思想。
福谷以陈亮三个时期的著述《六经发题》、朱陈论争、《勉强行道大有功》为例,指出这些时期陈亮有着ー贯的主张。此中,尤其重要的发现是,一般认 为完全水火不容而告终结的朱陈之论争,实际上陈亮接受了朱子的部分说法, 对自己主张加以修正改变。
陈亮在这场论争中,主张汉唐君主的政治中天理并非总是不存在(“无常泯”)。[⑹与此相对,朱子反驳陈亮的说法,认为天理并非总是不存在(“无常 泯”),也就意味着存在没有天理的时候(“有时而泯”)。[17]
陈亮接受朱子的批判,主张三代圣王和汉唐君主虽然“本领(根本)”相同,但因为有“工夫”的差别,因而王道的完成度有差异。[⑻也就是说,陈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汉唐不是理想的王者,他们的“工夫”不足。这是陈亮在与朱子论争之前不曾有的主张。但是,在这ー论争中,陈亮完全没有言及关于 “工夫”的具体内容。
对此加以论述的是陈亮晚年的著述《勉强行道大有功》。福谷指出,在该文中,陈亮阐述道: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抱持“喜怒哀乐爱恶”的感情,而是与万人共有该感情,就能够实现王道政治,故将之题名为“勉强行道”。又说,正因为不能做到这一点,汉武帝虽然英明,也不能成就如三代圣王般的功绩。[19]
福谷通过全文的论述,将陈亮的思想做了如下总结:陈亮认为追求包含自己在内的万人的利益为“义”,只追求一己的利益为“利”。陈亮的这一思想,与朱子形成鲜明对比。朱子认为“无所为”的动机的纯粹性为“义”,盘算追求利益是“利”,消除盘算“利”之心,才能生发出止无可止的道德心的“义”。与此相对,陈亮认为,谋求并非一己而是万人之“利”的公共性即是“义”。如此,朱子和陈亮对“义”和“치」”的理解不同,朱子对“义”“利”的理解是二律背反,而陈亮认为扩大“利”的受益者就是“义”。福谷指出,这样以利益的公共性为核心的陈亮的义利观,是以《孟子》中游说统治者施行王道政治取得 治理政绩的记载为根据的。[20]
根据以上论述,福谷在该文的结论部分指出,以追求自身利益之心为岀发点的陈亮的思想,具有鼓励追求万人利益的特色,这ー想法,挖掘出与朱子不 同的解释《孟子》的可能性。
三、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知,2017年与2016年一样,狭义的朱子学研究不多,对朱子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一起加以考察的论著较多。又,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擅长精细的经学研究和踏实的文献学研究,类似下川玲子氏《朱子学から考える権利の思想》这样旨在重探朱子学现代意义的著作,则是很稀有的尝试,今后研究者也 可以在这一方向上多加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伊东贵之编《“心身/身心”と環境の哲学:東アジアの伝 統思想を媒介に考える》和细谷惠志著《薛環と明代朱子学の研究》两书均为 2016年出版的著作。因笔者的疏忽,2016年的研究综述中未予以介绍,因此, 将编入本年度的研究目录中。敬请读者朋友谅解。
(作者单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
2017年度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在过去一年,美国有不少涉及朱子学的研究。本报告将按专著、论文、会议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排序对有关成果逐一介绍。
一、专著
刘纪璐教授(JeeLoo Liu)于2017年出版了其新著《新儒家:形而上学、精神与道德性》(Neo-Confucianism:Metaphysics,Mindand Morality)。[1]该书集中分析了数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全书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新儒家形而上学的思想,共收入四篇论文。第一章讨论了周敦颐“无极”和“太极”的概念,以及其“无极”的思想与以前“无”的思想的关系。第二章分析张载的气论,指出张氏把“气”引入其形而上学和道德学说之中。第三章主要考察二程与朱熹的形而上学。作者讨论了在他们的哲学体系当中,自然是否偶尔生成,抑或其中存在着一个法则?通过将他们的形而上世界观注释为规范的现实(normative reality),作者指出三人都将天理视为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法则,其中总体的法则主宰着个别的事物。第四章则将焦点放在王夫之如何发展气论。她认为王夫之是新儒家气论与天理的集大成者。在其理论当中,自然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是浑然为一的,两者都被气与天理所支配。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新儒家学者的道德思想及人性,以及各人的分歧。第五章首先考察了朱熹的人性论。作者指出于朱熹而言天理或太极是世间最高的法则或标准,而它们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道德准则也是以天理为依归。第六章则讨论了陆象山和王阳明的道德观。作者指出两人均有别于程朱学派,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或将人的思维看成是天理本身。第七章则分析了王夫之有关人性的论述,其中气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气是变化无常的,故人性也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且受人的感情和欲望等影响。
该书的第三部分以当代的伦理学和心理学来剖析新儒家学者关于人性与道德的思想。第八章以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为出发点分析张载的道德哲学,并认为张载主张人的道德是一步步,自发地发展而成的。第九章指出有别于张载,二程认为人的道德于不同处境之中都是相同的。而他们的教育便是要培养人们这种道德感。第十章探讨朱熹有关如何成圣的思想。她以道德认知论为视角,讨论了朱熹如何鼓励人透过对个别事物、人性的理解去掌握天理。第十章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视为一种“较高级的感知”(higher-order perception)。以道德反思论(moral reflflexivism)为基础,她认为王氏的良知说是指人具有自我管束与纠正的能力。第十二章分析了王夫之的社会伦理学。根据她的描述,王氏并不认为道德可与社会割裂。社会对人的道德成长有一定影响。
二、论文
除专书以外,2017年亦有数篇涉及朱熹的论文出版。首先,田浩教授(HoytCleveland Tillman)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学生对当代朱子婚礼的看法》(“Reflflections on Chinese Student Opinions on the Modernized Zhu ConfucianWedding”)的论文。[2]这篇论文收录在《日常生活以外:纪念何尔曼教授六十五岁大寿论文集》(UberdenAlltaghinaus:Festschriftfurthomas O.Hollmannzum 65.Geburtstag)之中。这篇论文可说是数年前他与女儿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合撰之论文的延续。[3]田浩教授在文中通过分析和比较从中国几所大学的大学生之中所得到的数据,来探讨现代学生对于经朱杰人教授改革后的朱子婚礼的看法。这些大学包括南方的杭州师范大学、北方的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作者在2010年的文章中对后三者已有详细的分析,故此文只概括其中的调查结果以做比较之用)。以下是一些在调查中值得留意的地方:
(1)性别差异对学生接受有关礼仪与否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杭师大的受访女学生较留意仪式的美感,受访男性却不太在意仪式美丽与否,更着重其对家庭的重要性。
(2)大多数受访者(不论是南方或北方)都不认为经朱杰人教授改良的朱子婚礼的美感足够使人们接受和采用。
(3)受访者认为仪式当中所朗读的古文会令人却步。
(4)尽管受访者希望有足够的自由度去安排婚礼,但他们仍希望父母(尤其是男方的家长)提供协助。这在北方尤为明显。据作者所言,多数北方大学的受访者认为婚姻非是单单两个人的事。
(5)调查显示南北两地学生观点上的一些差异。例如,南方的学生普遍不认为朱杰人改良的朱子婚礼与传统差距很大,可是北方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则认为他的版本与传统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推断这可能反映了北方大学生对 传统的喜爱,而南方学生较重视美感。不过作者也指出,调查仍未能全面反映 相关的地域差距。
尽管作者在文末强调有关调查有其局限,但他认为,朱杰人教授或其他人 在推广传统婚礼时,有关数据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Eiho Baba亦于《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发表 了《“矢口觉”在朱子哲学中作为认知与理解能力:通过“魂”和“魄”所作的 一・个考察》(“Zhijue as Appreciation and Realization in Zhu Xi: An Examination through Hun and Po")一文。"’这篇文章通过“魂”和“魄”这两个概念考察“知觉”在朱子哲学体系中的意思。作者认为,“知觉”是ー个精神物理学上的过程。它拥有一种能对不同环境和各种复杂的关系中的正确行为做出认知性的 评价的能力。作者继而指出,“知觉”并非ー种对既定事实的被动性的感知。相 反,它是ー种能参与对世界进程做出决定(participatory co-determination of the world)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通过对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训练来获得的。
又Larson Di Fiori和Henry Rosemont合撰之《论〈论语〉中的仁》 ("Seeking Ren in the Analects")亦引用了朱熹有关“仁”的解释。仁的意思历来均为研究《论语》者关注的课题之一。此文认为在阅读《论语》时,人们不应将孔子视为ー个意图建筑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而应将之视为一位希望教导 学生的老师。因此,我们应以学生如何与孔子讨论仁作为切入点来理解仁这个 概念。文章中段提到朱熹的注释也注意到孔子在论仁这个概念时会因情况而做出改变,而孔门学生在其中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仁并非ー个抽 象而绝对的标准。相反,它是个人与他人相处时的行为准则。
三、会议论文
在2017年10月份,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estern Branch)年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其中有两篇报告讨论了朱熹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书信来往。第一篇是《朱熹与陈亮书信中的抱膝诗》(ル函 on ''Embracing Knees ‘‘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Zhu Xi and Chen Liang),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课程的博士生黎江南(Li Jiangnan )。这篇文章议论了朱熹和陈亮在利用书信往来时,陈亮希望朱熹为他写一首抱膝诗的事件。作者认为这起事件反映了两人对诸葛亮态度的转变,和指出朱熹试图与陈亮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考虑到朱熹本身的知名度以及信件在当时流传的程度,作者认为朱熹在这件事情中使陈亮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此,对这起事件的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二人辩论的内容,以及将他们思想上的转变与社会因素和其语言使用的方法结合起来一同思考。
另一篇报告题为《送信的方式及其对文人交流的影响:以朱熹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为例》(“The Way of Delivering Letters and Its Impact on Communication:ACase Study of the Letters between Zhu Xi and Others”),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任仁仁(Ren Renren)。通过分析约2900封朱熹与其友人所写的信件,他在报告中指出他们主要利用三种途径去送信:通过官方的邮寄系统(附递);通过专人送信;最后为通过学生或朋友送信。作者指出上述各种送信方式对于文人沟通而言有一定的影响。
四、学位论文
2017年美国大学共有两篇博士论文与朱子学研究有关。第一篇是由Courtney R.Fu博士所撰之《文人与“地方”的建构:帝制晚期的泉州文人社团》(“Literat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Local”:The Quanzhou Community ofLea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6]这篇论文是对泉州所做的一个社会文化史研究。以该地区“清源学派”,即那些学习程朱思想的学者群为切入点,作者考察了该地区的文人精英与当地的关系。这篇论文指出“清源学派”的文人具有双重身份:乡绅与乡官。作为乡官,这些文人试图通过对将该地区的文化水平进行评估来把他们与帝国政府连接起来。当地朱熹的学术谱系以及后来的程朱学者因而成为了“清源学派”推动泉州成为当时学术中心的文化符号。而作为乡绅,“清源学派”的文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自认为得程朱学术之正统而不曾做出任何改变。事实上,为了保障其福祉与生计,他们会违反政府的禁令而进行海上贸易,并积极推广重商的价值观。可以说,这篇论文是研究朱熹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
另外一篇有关朱熹的博士论文为张蕴爽博士(Zhang Yunshuang)的《透视的私隐:宋代的书斋与空间》(“Porous Privacy:The Literati Studio and Spatialityin Song China”)。[7]她的论文考察了宋代书斋的空间性问题。她指出书斋一方面提供了私人空间予文人进行文学活动,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外开放予个别文人,让他们得以在内交流以及成为他们的身份象征。尽管朱熹并非该文主要讨论的对象,它亦介绍了朱熹对于书斋的一些论述。例如在第二章中,她描述了朱熹是如何讨论书斋与读书(道德修养)的关系,以及书斋的环境如何为他带来“至乐”的境界。同时,作者亦引用了不少朱熹所撰之文章、诗词和书信,如《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答许顺之》等。故此,即使这篇论文涉及朱熹的地方不多,但却让我们从另ー个侧面了解朱熹对于外在环境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关 系的看法,以及探讨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关系。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
2017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概况
〔德〕苏费翔
2017年,欧洲朱子学研究成果主要展现在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会上, 概况如下:
1.2017年9月7〜9日,欧洲中国哲学学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hilosophy, EACP )第二届双年会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召开。
欧洲中国哲学学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hilosophy, EACP ) 由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University of Ljubljana )汉学教授罗亚娜(Jana S. Rosker )女士于2014年2月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创立,罗亚娜教授为首任主席。现任学会主席为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Vilnius University )东方研究中 心(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主任韦特斯(Vytis Silius )。该学会旨在鼓励并促进欧洲各国的中华哲学学术研究,为富有成效的合作与思想交流创建并提供平台,开辟亚洲特别是中华思想史方面学者之间的对话,为当前领军学者的发言 与探讨提供平台。
年会上,有关朱子学的报告主要有:
Maud M 'bondjo (卓楚德,法国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德 国埃尔朗根ー纽伦堡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Numberg ),发表论文“A Philosophical and 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date ( Ming ): The Case of Zhu Xi(1130〜1200)”(《哲学与卜筮学对“命”的解释ーー以朱熹为例》),详论朱熹对“命”概念的见解。作者综合《朱子语类》“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与《周易本义》将《易经》视为卜筮书的基本看法,分析朱子读书、静坐、卜卦的工夫,强调朱熹虽然接受大们卜筮的习惯,但是自己却极少算卦问命。
Fr6d&ic Wang (王论跃,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〇),发表论文 "The Notion of Ming in the Beixi ziyi by Chen Chun ( 1159 ~ 1223 )”(《陈淳〈北 溪字义〉论“命”》),强调“命”为《北溪字义》首段的主体,而要研究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过,王老师没有找出哲学理由,而是猜测与《近思录》的结构有 关,从而推论陈氏把《北溪字义》视为口授哲学伦理的教材。
Margus Ott (熊古思,爱沙尼亚的年轻学者)发表论文"A Deleuzian Perspective on Zhu Xi"(《从德勒兹的角度来论述朱熹》),用著名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 1925〜!995 )的本体论思想来发挥朱熹的理气论与大极思想。Christian Soffel (苏费翔,德国特里尔大学)的论文题目为"Mystical Elements in Zhu Xi's Cosmology: The Notion of 'Empty Soul-Consciousness (《朱 熹宇宙论的神秘色彩:“虚灵”的概念》)。论文以朱熹在《大学》《中庸》中出现的“虚灵”ー词为出发点,介绍朱熹把“虚灵”视为人心的特征,朱熹的弟 子(如黄榦、陈淳)进ー步加以说明,使“虚灵”成为学术专有名词。
此外,Vladimir Glomb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发表论文“After Zhu Xi: Kor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otong"(《朱熹之后韩国的道统说》),Martin Gehlmann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发表论文“Zhu Xi's White Deer Grotto Articles of Learning as Educational Philosophy"(《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的教育哲学》)等。
2. 2017年9月14~ 17 H,第二届“唐至明中国人文会议”(Second Conference on Middle Period Chinese Humanities )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
此次会议由魏希德教授(Hilde De Weerdt)和何安娜教授(Anne Gerritsen )共同筹划举办,吸引了来自欧、美汉学界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的关注,参会学者超过百人。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史 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探讨从唐代到明代的中国人文。
朱熹作为宋代著名思想家,对其思想研究者甚多:Joep Smorenburg (荷兰 莱顿大学) "Zhu Xi's Military Thought: Utilitarian Perspectives on the Jin-Song Conflict”(《朱熹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对女真金与宋人冲突的看法》),Kim Youngmin (首尔大学)-"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Theory: Revisiting Zhu
Xi's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经注与政治理论:重谈朱熹的四书章句 集注》),汤元宋(北京大学)——《〈朱文公文集〉未收书信原因考释—— 元两朝文集所见朱熹书信真迹题跋为线索》,祝平次(台湾“清华大学”)—— 《邵雍、张行成与朱熹》,任昉(德国特里尔大学)ーー《赵秉文之〈道德真经 集解〉及其学术源流》,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德国特里尔大学)—— "Reexamining the Topic of Shendu in Confucian Traditions from the 13 th Century"(《重谈!3世纪儒家学派的慎独论》)等。
(作者单位: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蔡方鹿 赵聃
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他吸收并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思想,从而建立了“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2]此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这些思想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朱熹的思想体系。虽然理学与文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为数众多的经学家兼治文学,文学家亦擅长经学,而经典本身又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文学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3]朱熹将经学义理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点。正如钱穆所说:“轻薄艺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应共赴之标的。”[4]因此,这里很有必要清理一下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或可为朱子学提供一个“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视野。
一、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研究
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其文学著述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两部著作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相关问题上。另外,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朱熹理学与其《韩文考异》关系的研究。
(一)理学与《诗集传》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诗经》彻底脱去了‘经典’的神圣皇袍,而被认作是一部诗歌总集。”[5]朱熹理学与《诗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地被学界所关注。1919年傅斯年提出:朱熹的《诗集传》虽然还有几分道气,但具有“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的特点。[6]1928年他在《泛论<诗经>学》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部书(《诗集传》)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7]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一书中认为:“朱熹论《诗》,如更进一步,超脱宗教性之经学,而立场于纯文学之观点,则一切新说适足以显其伟大的创见;奈其说仍局促于经学桎梏之下,仍以伦理的观念为中心,则何怪乎责难者之纷来。而吾人于此,亦可见经学与文学自有其不可混淆之封域矣。”[8]与此同时,郑振铎也认为,朱熹“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9]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多是点到为止,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港台学者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钱穆认为:“朱子以文学方法读《诗》,解脱了经学缠缚,而回归到理学家之义理。”[10]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熹理学与《诗集传》关系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主要集中在《诗集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是对“淫诗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义理时,涉及“淫诗”与义理及人情的关系,这与《诗经》的文学性相关。如谢谦说:“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沟通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淫诗’之说能够在经学范围内成为可以‘自圆其说’的体系。严格说来,朱熹不是发现了《诗经》中有‘淫诗’,而是从理学角度完整地阐述了‘淫诗’为教的经学意义。”[11]认为朱熹将“淫诗”纳入了他的理学体系来阐述他的诗教思想。另外,赵沛霖、吴正岚、谢海林等对此也持相似的观点。[12以上学者认为,朱熹的《诗经》研究虽然涉及“淫诗”这一文学性的特点,但本质上朱熹是站在理学的角度来阐释《诗经》的。台湾学者姜龙翔亦云:“朱子对淫奔诗的界定虽是由其理学思想出发,否定诗人情性,进而对于民歌抒发自由情感的本质有所误解,但经由朱子的论述,却较汉学将《诗经》视为国史代言创作的产生论,表现出多元的解释。”[13台湾学者黄景进从朱熹的心性哲学出发做了研究,说:“朱子根据其心性哲学,认为情有善有不善,故诗亦有正有变,由此认定《诗经》中有‘淫诗’(淫诗所表达的是不正的感情),并反对‘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说法。”[14]
二是认为朱熹以文学解《诗》,突破了理学的束缚。美籍学者杜维明在《朱子解诗》中说:“朱熹把《诗经》视为美学思想的源泉和道德训诫的宝藏而加以认真研究。……朱熹认为在客观地分析诗以前必须朗读诗和体验诗的意境。”[15]这也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读《诗经》。莫砺锋认为:“朱熹著《诗集传》,其本意也是从事经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悟性,其治学态度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所以他对《诗经》文本的文学性质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诗集传》在实际上终于打破了经学的藩篱,《诗经》学终于在一位理学宗师的手中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16]汪大白说:“朱熹正是在他的理学宗旨与文学意识紧密结合和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研究直接影响并实际革新了旧的经学研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诗经》学发展史的根本性转变。”[17]另外,檀作文、李士金也对此发表了相似的论述。[18]以上学者认为,朱熹是在阐发《诗经》理学思想的过程中,“以《诗》言《诗》”从而促进了《诗经》文学性的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朱熹研究《诗经》的方法是分不开的。蔡方鹿以朱熹的读书法为切入点,认为:“‘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文学的功能在于抒情,诗人言《诗》,则‘发乎情’;其理学的要旨则在于阐发义理,理学家说《诗》,不离理与性善。朱熹既重《诗》文之言情的本义,又重义理的阐发,因此可以说,朱熹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情与理、情与性的结合。”[19]并指出:“朱熹客观地看到古人作《诗》是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突出一个‘情’字,认为抒发感情和自然情感是诗人作《诗》的本意。同时,朱熹也注意把吟咏情性与玩味义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20]分析了文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郝永以《二南》为例分析了朱熹二《南》解释学中“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矛盾性”。[21]]台湾学者陈昭瑛则“尝试建构朱子的诗学及其与儒家诗学的关系”,“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脉络来掌握朱子诗学与儒家诗学的现代意义。”[22]
三是把朱熹的《诗经》学与经典解释学结合起来。邹其昌从诠释学美学思想的角度认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由‘以《诗》说《诗》’所开启,历经‘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之磨炼,旨在获得‘性情中和’之境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转折意义的典范。诗经诠释学由此逐渐走出‘经学’,走向真正的审美!”[23]即朱熹在对《诗经》的诠释中认识到了其中的文学性。曹海东认为:“就朱熹的经典解释活动看,他可以说是很好地践行了上述解释学原则。对《诗经》的解释就是一个显证。”[24]这些原则包括据诗之情实自出新解,把训诂释文义与讽诵见道理相结合,即在《诗经》诠释中,把文学与理学结合起来。郝永则系统地对朱熹《诗经》的解释学进行了研究。说:“朱熹解释《诗经》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其文学特质的重视,二是对其理学价值的发掘。两者都是对汉唐经学以美刺解《诗经》的大突破、大发展。”“故朱熹的《诗经》解释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既有文学的维度,也有理学和史学的维度;既是对经学旧说的继承与扬弃,也有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总之,朱熹《诗经》解释学是以理学为旨归的多维度的经学体系。”[25]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一角度对朱熹的《诗经》学进行研究,我们要清楚的是,理学与文学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的分类下产生的,“然若从贴近古代情状的视角观察,从前儒者的经典诠释活动,也可能透过类同文艺批评的形态发生,特别是在向以艺术性见称的《诗经》身上,朱熹的《诗集传》或者就是个典型案例。”[26]因此,我们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不能割裂其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应从理学、文学二元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和把握朱熹的《诗经》研究中理学与文学间相分相合、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理学与《楚辞集注》
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其著作《楚辞集注》一书中,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朱熹的《楚辞集注》展开。朱熹的楚辞学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有学者认为:“朱熹最早彻底地以文学眼光看待楚辞,他自觉抛弃了楚辞研究中的经学标准,抓住了楚辞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27]也有学者认为:“朱熹在鉴赏楚辞的时候,的确是把‘情’字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只要理智稍胜感情,便要流露他道学面孔,立刻会对情字加以限定词,要求情必须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28]实际上,朱熹的楚辞研究并没有抛弃经学、理学的标准,这一点学界多有讨论。韩国学者朴永焕认为:“朱熹在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理论基础上,主张实行以道为本的判文、以理为准的评诗、以古为法的复古思想。”[29]并且这些文学思想强烈地影响了《楚辞》的研究。束景南也认为朱熹在注解《楚辞》时“用理学的‘文化范型’重新铸造屈原的历史形象”并“把作为游艺之学的文学也拉回到理学的轨道与框架中去。”[30]孙光从篇目选择和体例确定、文本注释、屈原思想的阐发、楚辞艺术的观照、注释特点五个方面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的关系。他认为:“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使其在注释中既遵循理学价值标准阐发义理,又能够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31]罗敏中从朱熹的“尊屈倾向”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32]李士金则研究了朱熹将理学思想引入楚辞研究的原因,认为:“朱熹把他的理学思想引入《楚辞集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南宋科技水平进步之结果。”33另外,还有学者对朱熹的辞赋观做了研究。何新文认为:朱熹的辞赋批评“明显具有以道德哲学标准否定文学的偏见。”[34]这在注释篇目的选取上也有体现。莫砺锋认为《楚辞后语》对作品的选择受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理学家的迂腐性。[35]于浴贤、徐涓、台湾的梁升勋对此也做了考察。[36]虽然以理学的标准来选取篇目确实会遗漏一些好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就此来研究朱熹的辞赋观和文学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学者,多从朱熹的理学思想出发来论述理学对朱熹楚辞学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理学阐释方法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肖伟光认为:“《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37]徐涓从格物致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格物’结果是‘物格’与‘知至’,亦即求得事物义理之豁然贯通,对《楚辞》而言,就是兼得其‘性情’与‘义理’。”[38]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集注》及楚辞学关系的研究多从理学对楚辞学的影响着手,而很少注意到《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对于朱熹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朱熹在评价《楚辞》时多是义理性与文学性兼有的。如据《楚辞集注》载:“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39在这里,朱熹把阐发君臣之义理建立在承认《楚辞》“陈情”感怀之言情性的基础上,可见文学对理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朱熹《楚辞》学的研究,不能忘记朱熹理学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和朱熹《楚辞》研究理学与文学兼顾的特点,应从理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入手,找出二者的联系。
(三)理学与《韩文考异》
对于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的研究,学者们多把《韩文考异》当作朱熹校勘学的代表而研究其校勘学意义。吴长庚认为:“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法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40]朱熹的《韩文考异》中确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但朱熹并不是为了校勘而校勘,他是借助韩文的校勘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的。正如钱穆所说:“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然则校勘虽小业,于义理经术史学文章靡不有其相关互涉之处。后人仅知从事校勘,又何能望其津涯,而窥其底蕴。”[41]可见,朱熹理学与《韩文考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束景南认为:“朱熹在党锢中选择韩愈文集做考异的目的又不仅是为了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个大文豪的威望来巧妙宣扬‘道学’的深意。贯串在《考异》中对韩愈批判的一面,便渗透了他的道学‘伪气’。”[42]
二、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研究
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有文道观、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等四个主要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如蔡方鹿、王哲平等。蔡方鹿认为:“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道合一,‘即文以讲道’和诗理结合的思想。其理学与文学并行不相悖,可以互相结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与只重理学而轻视文学的理学家相异,同时也表明理学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文学的桎梏,尽管理学有抑制文学的倾向。”[43王哲平从文学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做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44]李春强则从理学著作《论语集注》出发综合研究了朱熹的文学本体观、创作观等文学理论。[45]
(一)文道观
张立文指出:“文道关系论是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文道关系论的展现,便是诗与理的关系。”[46]台湾学者杨儒宾也认为“朱子说‘道之显者谓之文’,‘文’与‘道’可视为一体的表里关系,这当视为理学家另一种对文学重要的界定。”[47]可见,朱熹文道观也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对于这一论题,学界的主要看法是“文以载道”或“文道合一”。“文以载道”论以周予同为代表。他说:“朱熹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亦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如皮附以今日流行之文学术语,则朱熹或可称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48]此外,朱东润、陈千帆、台湾学者张健、钱穆等都持相近的观点。[49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持“文道合一”论,他认为:“文学不是‘道’的从属物,而是持有自身根据的自立之物。文学存在着自律性,植基于‘气’(气象)的发动,在这种根源性中文与道合成一体。”[50]吴长庚认为:“文道合一是建立在文与道二者并重,各不偏废的基础上,并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总结。”[51]对此莫砺锋、吴法源也持相同的观点。[52束景南进一步认为:“朱熹通过曾巩融合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思想学问路数,统一了道统与文统。”[53]值得一提的是,程刚从“理为太极”的太极观出发来讨论朱熹的文学本原论,认为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本论的哲学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一方面延续了文从道出的本原论,以文为工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于程颐‘作文害道’的一个修正。”[54]
(二)理学与诗论
郭绍虞指出:“朱子论诗不唯集道学家之大成,也且兼诗人之诗论而有之了。”[55]对于朱熹理学与诗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理学思想对其诗论的影响上。一般认为,朱熹诗论的基础态度是“道学是第一义的当行职责,做诗是第二义的感情辅助”,“诗歌的首要第一条便是义理纯正,所谓‘诗以道性情之正’。”[56]马积高亦认为,朱熹的诗论“强调诗人的主观动机要合于所谓‘性情之正’才行。”[57]以上学者的观点都看到了理学对于朱熹诗论的影响。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进一步认为:朱熹“以儒家心性理论为基础的诗歌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要求诗歌创作将情感体验与性理规范统一起来,成为作者道德人格和高远胸襟的流露,具自然平淡的‘中和’之美。”[58]石明庆讨论了朱熹理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影响其诗学的主要有理本气具的理气论、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居敬穷理的工夫论,以及心与理一的境界论等理学思想。”[59]另外,台湾学者黄景进从美学的角度对朱熹诗论进行了研究。他说:“大体而言,当朱子在论《诗经》时,他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发挥儒家传统的诗教观为目的;而当他在评论历代的诗人时,却较注意诗人在美学方面的表现。”[60]
以上学者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楚朱熹理学思想影响下的诗学理论。这也启发我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评价朱熹诗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朱熹的诗学理论是宋代理学家诗论中最有价值的”,“他论诗的许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珍视,其保守的一面则应予以扬弃。”[6[
(三)理学与古文理论
对于朱熹理学与古文理论关系的研究,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台湾学者何寄澎认为朱熹文论的“一切观点(包括文学性的观点)悉以道学为归趋。见证了朱子文论一方面是更道学化的;一方面却又是更包容而圆融的。”[62]闵泽平认为:“朱熹的文章理论虽带有浓厚的道学色彩,其间却颇多精辟的见解。他也重道轻文,但其观念远比周、程等人通达。”[63]
(四)理学与作家作品批评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除以上三个方面外,也有学者对朱熹的作家作品批评进行了研究。如踪凡认为:“朱熹论两汉诗赋,手中拿着两大标尺:一曰道德,二曰真实……他由此出发而得出的扬贾抑马,尤其是贬斥扬雄的结论尤其让人不能信服。”[64]全华凌论述了朱熹以“道”来评价韩文的得失。[65]黄炳辉认为朱熹的唐诗批评其精辟处在于道学和文学的统一,其瑕疵处“是以道学家的眼光代替诗艺术本身的观察。”[66]莫砺锋对朱熹的作家人品批评做了研究。认为:“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极为关注作家的品德修养。”[67]李士金则对此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朱熹“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68]谢谦全面地考查了朱熹的文学批评,他说:“朱熹正是根据这一新的价值标准,对《诗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的阐释与评价,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批评的模式。这个‘以理说诗’的道德批评模式同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史证诗’的历史批评模式一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69]以上学者研究的多是朱熹理学对某一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虽然不乏深刻的论述,但却缺乏系统性。另外,学者们多关注的是朱熹理学对其文论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文学理论是他理学思想的反映,及朱熹文学思想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论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在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某一文学理论,较少系统地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很少讨论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作为朱熹文学思想基础的文道观对他的诗论、古文理论、作家作品批评的影响。
三、朱熹理学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
1929年,周予同在《朱熹之史学与文学》一文中指出:“朱熹之文学作品,诗赋散文,各体均有。然韵文喜插入说理之语,每使人深感酸腐之气……朱熹在文学史上之所以尚能取得一地位者,在其说理之文与解经之文。”[70]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诗歌与文章创作两个方面。
对于朱熹诗歌创作的研究集中在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上。胡明认为:“朱熹作为一个道学家,他的诗却绝少道学气,更无头巾气、酸馅气。”71郭齐认为:“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72]许总对朱熹的创作实践做了分析,认为:朱熹的创作实践“即使是为了说明治学之理,亦全借优美的自然意象表达出来。正因这类‘不腐之作’,朱熹诗被后人称为‘道学中之最活泼者’”[73]。莫砺锋亦认为:“朱熹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丰富生活情趣的诗人,这种独特的素质使他成功地消除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并进而使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74]李育富研究了朱熹易学思想与其诗歌关系的互动,说:“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75]吴长庚则“从朱熹解易解诗之思维程序、方法、原则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朱熹的解诗思维中,他致力于诗歌比兴形象的发掘,寻求诗歌感发性情的活的功能,力求通过正确的诗解,建立一套开放性的解诗思维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易解思维中之积极成分的”。[76]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朱熹诗中的理学思想。美籍学者陈荣捷在《论朱子<观书有感>诗》一文中解释了诗中词语的理学含义。[77韩国学者李秀雄认为:“朱熹作诗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诗本身的艺术形象。他使诗中的理和趣互相和谐而达到交融的境界。”[78]日本学者申美子在《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朱子数量庞大的诗作,正是研究其一生思想形成、转变、发展极其丰富而真确的材料”,并从朱熹的诗作出发,“探讨其一生学问思想的发展轨迹”。[79]石明庆也认为,朱熹的诗歌“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80]。在朱杰人看来,“朱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抑或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对宋代的诗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公正的、充分的估价”[81]。胡迎建亦云:“了解其理学与诗歌的关系,有利于理解其诗。”[82]这同样也能进一步了解朱熹的理学思想。
对于朱熹理学与文章创作关系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饶宗颐对朱熹的文章做了研究,认为“朱子说理之文,逻辑性特强,又覃思者久,增、减不得,极得洗伐工夫”[83]。莫砺锋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他(朱熹)的散文写得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他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理解理学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窗口”[84。而闵泽平则深入地探讨了朱熹理学与其文章创作的关系,认为“朱熹行文的从容、平和,首先来自于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对义理的体认与把握,来自他道学气象的自然流露”[85。方笑一将朱熹的经学与文章之学相结合,认为:“与北宋儒者不同,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86另外,王仕强认为:朱熹“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87]具有典范意义。黄拔荆、周旻则“分析了朱词与其文学观、理学观的关系”[88]。许总则对朱熹理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说:“朱熹将‘义理’与‘诗文’加以遘合,表明了对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89]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明了理学对朱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以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的朱熹的文学作品。另外,通过分析研究朱熹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究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理学与文学是怎样融合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这也是朱熹文学作品对于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特殊意义。
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展望
通过以上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是开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学与《诗经》学、文道观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但研究成果多为简要的概括式论述,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港台及海外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虽然百年来学术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以至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比较而言,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进行,尚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做出一个融会贯通、整体综合性的系统研究。由于朱熹思想本身就是由文、史、哲,儒、佛、道等相互贯通而构成,朱熹理学与文学是统一于朱熹思想的一个整体。因此,研究朱熹理学不及文学、研究朱熹文学不及理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一些学者,对朱熹理学与某一方面的文学做过个案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未注意把朱熹理学与文学作为整体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故未能揭示出朱熹理学与文学之总体特征,因此也不能进一步说明朱熹理学与文学之关系。所以目前的研究情况与朱熹既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尽管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目前的研究,确实是朱子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需要改进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高。在这个新的视域下,去挖掘朱熹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实质及所体现的朱子学的特点,而不是以往大多就事论事地分论朱熹的理学和文学,从而澄清和阐明朱熹理学思想中的文学性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回答其理学怎么通过其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而其理学思想里又具有哪些其他理学家不曾有的文学性等问题?从而客观揭示朱熹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及情理结合的特征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既对深入研究朱熹理学有利,也对深入研究朱熹文学有利,更对全面、综合研究朱子学有利。因此,站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朱熹思想及其价值、地位和影响,对于学术界完整理解朱熹的整个思想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我们以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为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进而展望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开展:
(一)朱熹思想是在致广大、尽精微,涵盖、吸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打破界限,以融会贯通的视角去研究朱熹思想。这也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学科学术研究之间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时代要求。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将朱熹的理学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仅以此促进朱子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而且拓宽了研究领域,这对朱子学的研究很有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应将具体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由于朱熹文学是由《诗经》学、楚辞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等多方面构成,我们应以这些具体的研究为基础,运用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散到联系、从局部到整体的观点和思路,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展开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并加以概括提炼,从而对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系统的认识,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推动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文化史上伦理与自然之争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尚伦理、重教化与崇自然、重情感两种文化价值观之争,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价值。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对其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其理学思想中的尚伦理、重教化与文学思想中崇自然、重情感是怎么统一于朱熹思想中的,它们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的融合又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研究的展开将为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创新的视角,同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儒学与文学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及所体现的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亦是朱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所要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某一学科的创新。某一理论学科的成就,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先导。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应采用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融合互动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上,应采取点、面、线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把朱熹理学与文学置于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以朱熹理学与文学为点,以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和盛行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为面,以整个中国经学史、文学史、理学史等所构成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结合,在相互联系中,做纵横比较,分析探讨,深稽博考,融会贯通,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朱熹理学与文学及其在中国经学史与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和作用。
(四)在研究工作中,应将理论分析与训诂相结合。既要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把研究建立在考证、训诂、细读深研文本,弄清掌握朱熹经学、文学著作本义的基础上,又要避免单纯的训诂考证,而忽视对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及其思想性的深入、深刻表达。
以上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仅是我们的一点意见。希望通过以上的评述和论析,在以往研究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拓展,站在朱子学促进、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时代高度,以创新的方法、理论和新视野、新材料的挖掘运用,为朱子学的研究,在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影响、结合的视域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新展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世纪以来张栻思想研究述评
蔡浪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当时学者陈亮评价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1]“荆州”即是指张栻,故又有“一代学者宗师”之赞誉。张栻是1160年左右最有影响力的道学家[2],在老师胡宏去世后,成为湖湘学派领袖,使湖湘学派思想发展成熟,造就了“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3]的盛况。《宋史·道学三》卷四百二十九[4]中将张栻和朱熹两人并列一传,肯定了张栻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一直是既热门又重要的研究课题。张栻对朱子学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在朱子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陈来先生曾说:“张南轩是朱子学前期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5]然而,对于张栻的研究,却长期被学者所忽视。整体而言,作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朱子学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张栻在日美韩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大陆关于张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虽然目前对于张栻的研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很大拓展和进步空间。现就张栻国内外研究概况、生平与评价、交游、理学、经学、实学与教育、回顾与展望等方面,对20世纪以来张栻思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并略加评述。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在日本宋明理学界研究中,张栻乃至湖湘学研究,皆属于边缘化课题。对张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高畑常信先生表现最为突出。高畑常信先生师承友枝龙太郎,专注于张栻以及湖湘学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了有关张栻《论语解》、张栻思想的变迁、与朱子论未发已发以及仁说等思想研究的成果。1996年,高畑先生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出版《宋代湖南学の研究》[6]一书,这是日本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研究湖湘学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少有人再专门从事张栻思想研究的工作。从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日本的研究者们比较专注于从思想史及文献学的角度,对张栻的思想进行史料翔实的考辨以及细致的文献梳理,但在义利的诠释方面却有所欠缺。
在欧美,对张栻包括整个宋代思想研究,与汉学其他领域相比,呈现出起步晚、相对边缘化的状况。蔡慧清对欧美的汉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认为长期以来,欧美对传统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后延伸至秦汉,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西方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朱子学在内的西方宋学研究才逐渐繁荣起来。[7]有关张栻思想的研究,亦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才逐渐走入美国学者的视野。陈荣捷先生对打开美国宋学研究的新局面贡献显著。陈先生在对朱子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中,也涉及了对张栻的研究,却并未对张栻的思想价值与贡献做出其应有的评价。田浩先生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外在进路”的研究方法入手,在研究朱子的同时肯定张栻对道学形成的重要贡献,为国内学者研究张栻乃至朱子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切入点。虽然这些学者的努力,推动了张栻思想研究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南轩学作为朱子学研究下的一个边缘化课题的地位,在欧美国家并没有改变。
韩国学者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相比之下更少,还未出现过对张栻思想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多是在研究其他人物或问题时涉及。对于张栻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与朱熹联系在一起,涉及主题包括中和说、仁说、工夫论等。
在中国台湾方面,以往对于南轩学乃至湖湘学并无过多关注。湖湘学研究之所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要归功于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先生将宋明理学分为三系:伊川、朱子一系,陆、王一系,胡五峰、刘蕺山一系。[8]这大大提升了湖湘学的地位,以胡宏为首的湖湘学由此被重视起来。虽然牟先生将张栻排除在其分系之外,但毋庸置疑,张栻在湖湘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湖湘学不可回避的人物之一。于是,由于对湖湘学研究的逐渐关注与重视,张栻思想的研究也随之而展开。总的来说,牟先生对于张栻的否定,消解了张栻在南宋思想史上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张栻研究在台湾不被重视的基调。尽管这一局面在现在有所改变,但并无根本性的改观。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80年代初,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展开研究后,在受重视程度、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皆得到了迅速发展。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向大会提交专论张栻思想的文章,从各个侧面对张栻的生平学术活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张栻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张栻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9]这表明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已进入宋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并初步对张栻思想进行了探讨。
1991年蔡方鹿先生《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1]一书出版,弥补了学界张栻研究专著的空白。紧接着陈谷嘉先生《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11]出版,该书在理论论述上深入细致,其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湖湘文化的弘扬,并且将张栻放在与朱熹齐名的位置来谈他对理学的贡献,颇有为其理学地位正名的意味。由于这两本书的出版,张栻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
进入21世纪,对张栻的研究更是发展迅速。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四篇专门研究张栻的博士论文,分别是:苏铉盛《张栻哲学思想研究》[12],王丽梅《张栻哲学思想研究》[13],邢靖懿《张栻理学研究》[14],吴亚楠《张栻经学哲学论》[15]。苏铉盛和王丽梅皆是针对张栻的哲学思想,前者从仁说、中和说、心论、性论、敬论、知行论和义利之辨等问题入手,后者则从本体论、工夫论、人性论、义利观、知行观等传统框架来展开论述。邢靖懿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张栻的理学思想上,增加了对张栻经世思想以及排佛辟佛思想的阐述。吴亚楠则从经学和哲学结合的角度,对张栻的经学思想进行分析,重视他的思想中经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这些博士论文皆是研究张栻的专门成果,代表着张栻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会议论文集《张栻与理学》[16]和《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17]的出版,亦大大地丰富了张栻的研究成果。
此外,《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一书,将张栻经学与其理学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不仅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而且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18]而杨世文教授点校的《张栻集》[19],是现在最完整的文集版本。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张栻年谱》[20]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1]两本书。这两本书进一步弥补了张栻研究材料之缺。丰富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新材料的补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张栻生平与事迹,有助于张栻交游等研究开展,预示着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在未来将步入新的台阶。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张栻作为朱子学前期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重视。美国学者田浩虽然注意到了张栻的重要地位,但并没有改变张栻思想研究在欧美宋学研究中的边缘化地位。大陆对于张栻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其重要性得到大大地提升。但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和同期的朱子和吕祖谦存在差异,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生平和评价
研究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源流、学术传承以及影响与评价等相关信息,不仅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亦是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人物生平与评价的把握,更有助于思想研究的开展,以及更客观、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内容。
(一)生平事迹
朱熹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22],所载张栻传记翔实可靠。张栻的年谱比较晚出,一直到清道光年间宁乡王开琸辑刊《南轩公年谱》,才弥补了这一空白。另外还有民国时期胡宗楙编撰《张宣公年谱》,日本学者高畑常信的著作《张南轩年谱》,亦可供研究者参考。如今,这三本年谱由邓洪波教授辑校为《张栻年谱》[23],书中同时辑录了有关张栻的画像、传记、祭文、著作提要和序跋、纪念书院资料等文献,为学者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张栻提供了基本条件,为张栻思想研究带来了便利。
(二)学术源流与传承
胡昭曦先生对张栻的学术源流进行了系统清理。他认为张栻的学术师承主要是胡宏,除此之外还有孙复、司马光、邵雍、苏轼、谯定、张浚的学统,由于这种多元的师承,张栻在学术上得以集诸家之大成。其次,张栻的学术,植根于蜀,成熟于湖湘,其学术是蜀学和湖湘学的结合与发展。另外,张栻之学,经过他在蜀中的弟子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从湖湘返传回蜀,使正在继续发展的蜀学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学者,促进了蜀学的再盛,这是当时宋朝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
目前学界对于张栻学术渊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周敦颐、胡宏以及家学的继承与发展上。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鼻祖,在理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周建刚分析说,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发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周敦颐“道统”地位的强调;二是撰《太极解义》,从“太极为性”的角度诠释周敦颐的思想。[25]张栻师从胡宏,胡宏是他学术传承中最重要的一环。郭齐认为张栻在接受胡宏思想时,不固执一隅,采取唯善是从的治学态度。[26]钟雅琼分析指出,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27]家学亦是张栻思想来源的一部分,他一生陪伴在父亲张浚身边近30年,启蒙、受学乃至仕途皆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金生杨对张栻如何继承、扬弃张浚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释,认为透过张栻对张浚学术的继承与扬弃,我们更能体会张栻学术融会、由粗转精、由杂转醇之功。[28]
至于学术传承方面,张栻对湖湘学以及蜀学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对张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29]的评价,奠定了大陆学者评价张栻对湖湘学派作用的基调。陈谷嘉先生指出,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他对湖湘学派的发展无论从理论的发展,还是从传播湖湘学派的学术,皆贡献最大,他是继胡宏之后的唯一巨匠。30除了湖湘学以外,张栻亦是宋学中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夏君虞先生所说,他乃“蜀学的基石”[31]之一。杨东莼认为“南轩之学,盛行于湖、湘,流衍于西蜀”。[32]胡昭曦指出,南轩之学返传回蜀,推动了宋代蜀学的转型、“洛蜀会同”和宋代蜀学发展第二个高潮的形成;在南轩之学返传回蜀的过程中,宇文绍节、陈概、杨知章起到了倡导作用,其主要据点是沧江书院,而二江诸儒则是返传南轩之学的主力学者群。[33]
(三)影响评价
张栻“是否继承师说”“是否从朱熹转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一直是评价张栻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学者多认为张栻继承了师说,肯定张栻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全祖望早就指出:“张栻从朱熹转手,就好比说张载是从学二程一般,其实出自朱子后学捏造,不足为信。”[34]钱穆先生认为,“二人去短集长,交相师益,不必定说谁跟了谁。”[35]陈荣捷亦承认“南轩之于朱子,的是切磋琢磨之益友”。[36]蔡方鹿教授对张栻在哲学和理学上主要贡献的总结,代表了研究者们典型的看法。具体而言,主要贡献有三:(1)确立了集众家之长的湖湘学派;(2)在与朱熹的相互辩难中发展了二程学说;(3)论述并丰富了宋代理学的一系列范畴和重要理论。[37]不过亦存在不同的看法。牟先生认为张栻由于“受教日浅”,“未能精发师要,挺立弘规”,于朱子也“毫不能有所点拨”。[38]其弟子蔡仁厚先生进一步发挥师说,认为“南轩实乃五峰之不肖弟也”。[39]曾亦教授则认为,学术界素来认为南轩之学术因受朱子影响而发生改变,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40]
客观地说,1180年张栻英年早逝后,其在理学上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再也无法与朱熹相比拟。张栻学说后来之所以式微,李可心从心的出入问题加以观照,认为张栻的学术风格缺少应有的主动性和创发性,兼有理学和心学的特征而欠充分,且更偏重于实践性,以致逐渐丧失了在理学内部的话语权。[41]对于张栻在后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李英镐的一篇题为《吸收南轩学而产生之寒冈学的新理解——以寒冈郑逑的论语学为中心》[42]的文章。该文认为寒冈郑逑在重新诠释《洙泗言仁》的过程中,有吸收张栻的思想。这意味着张栻的思想对韩国思想家亦产生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其海外影响力,有待我们的发掘和研究。
近年来,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让学界开始重估张栻的地位和影响。田浩先生把“道学”的形成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二阶段把张栻、吕祖谦、朱熹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考察,认为他们的交往加速了道学传统的形成。[43]在具体时代背景下对张栻思想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考察后,田浩先生认为张栻对朱子的影响与贡献比以往学者想象的还要大。[44]这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张栻在道学乃至整个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张栻的思想研究也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发展。
三、张栻交游研究
与其他学者的交流和沟通,是张栻思想形成与完善的重要因素,道学亦是在这种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中形成的。书信是研究张栻交游最直接的研究资料。在书信编年上,杨世文、任仁仁以及顾宏义等学者,皆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仁仁和顾宏义两位学者,对张栻与同时代学者往来的书信加以汇编,考证其撰写年月,有益于南宋前期学术史、政治与党争研究、学人间交游情况等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5]杨世文教授除了对张栻写与朱熹的书信进行编年考证外[46,还对张栻诗文中关涉的若干人物进行了考证[47],这对于张栻诗文编年,以及张栻年谱的编纂,乃至研究张栻学术交游、学术思想演变皆有帮助。张栻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游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朱张二人的交往,另外还有些许有关东南三贤以及其他蜀学学者往来的研究。
(一)张栻与朱熹交往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山口察常于1938年发表了《朱子と张南轩》[48]一文,率先对朱子与张栻进行了考察。张栻与朱熹的交往研究,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张栻的交游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篇幅。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两人交往历程、朱张会讲、思想异同等方面。
综观张栻与朱熹的一生,两人仅有三次会面,其他皆以书信往来为主。陈代湘教授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49]
朱张会讲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世,开书院会讲制度之先河,成为书院自由讲学之先声,很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肖永明和谢川岭两位学者考察了历代学者对“朱张会讲”中朱熹、张栻地位前后的变化,认为这样一种叙述事实的变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过程。通过这种考察,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50]李清良和张洪志两位学者对“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进行了阐释,“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1]
在对张栻与朱熹交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是围绕两人思想争论进行的。陈谷嘉先生认为张栻和朱熹的个体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本体论上的分歧和争辩,二是中和之辩,三是仁说之辩。[52]陈代湘教授则认为朱熹与张栻二人思想存在异同,他们相同之点表现在性之善恶问题、心性关系,对仁的解释以及涵养识察之先后问题上。二人观点相异之处则表现在对太极的解释,对心的主宰性上。[53]田浩教授认为南宋道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朱熹的道学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他与张栻间气氛和谐的学术讨论中。在此,他选取了其中对道学同道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第一,工夫修养与“中和”问题,第二,《胡子知言》的讨论;第三个主要问题是“仁”。[54还有许多学者对张栻与朱熹之间关于太极、中和仁说以及察识涵养工夫论等思想展开了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些将在“哲学理论之探讨”一节阐述。
(二)东南三贤以及其他学者往来的研究
朱熹、吕祖谦与张栻在南宋并称为“东南三贤”,三者均为二程后学,他们的师承渊源有着密切关系。田浩先生对朱熹与张栻、吕祖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论述,强调朱熹之外的同时代儒家的重要性。[55]潘富恩先生对三人理学思想之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人思想上的异同,与二程有关。三者尽管学术各自有所偏重,亦有所分歧,但毕竟基本倾向是一致的。他们在互相切磋的过程中,都各自受到对方的启迪,增进了知识,使理学臻于精密、博大。对理学的发展,“东南三贤”各有自己的贡献。[56]此篇文章,后被高畑常信翻译成日文出版[57]。刘玉民指出,张栻与吕祖谦于《胡子知言》《论语》《孟子》《易传》《阃范》《仁说》等皆有学术交流,并于商榷中互相指正,切磋中互相提高。[58]
在与蜀地学者的交游方面,钟雅琼依时间先后之序,亲疏之别,论述了张栻与蜀地学者史瑶弼、宇文氏、范氏、丹棱李氏以及陈概等的交游情况,认为他的学术是理学与蜀学相融的前奏,他本人也在无意之中为“洛蜀会同”提供了助力。[59]此外,在张栻与南宋旧儒的互动中,邹锦良认为周必大和张栻的“知行”辩论反映了南宋时期旧儒学与新理学之间的歧异互动。[60]
四、理学理论之探讨
张栻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深,就理学特点而言,张琴认为张栻的学说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以太极为枢纽、以心为核心的由形上之本体世界向经验的现实世界展开的系统,其理学思想条理清晰,主旨鲜明,在理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在宋代理学运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61]在对南轩理学贡献褒奖之余,亦有批评的声音。郭齐认为张栻由五峰而直接周程,笃守有余而发明不足,略本体而详工夫,纯宋学而鄙汉唐,宽厚而少批评,稳定而少变化。[62]目前,学界对于张栻理学理论的探讨,概而言之,主要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以及伦理观等四方面展开。
(一)本体论
陈谷嘉先生指出,张栻构制了一个以太极、性、理和心等为基本范畴的具有层次性的本体论逻辑结构体系。[63]太极是张栻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其目的是为儒家伦理道德寻求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的根据。由于各种原因,张栻《太极解义》佚失不传。20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首先发现了《太极解义》逸文[64],为太极思想之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鲜为学界重视。直到21世纪,苏铉盛[65]、苏费翔[66]等学者皆对《太极解义》进行过辑佚与还原。目前,《张栻集》中附有复原的完整版张栻《太极解义》。[67]至于张栻太极说的具体内容,苏铉盛从张栻所著《太极图解》以及有关太极思想的种种观念和认识入手,对张栻太极说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其太极说之核心是以性释太极。[68]张栻之所以提出“太极即性”的命题,吴亚楠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69]李丽珠则认为两者在解经方法上存在不同:张栻以为阐述纲领即可,朱熹则以经学训传的方式系统注解其著作《太极图说》。这样一种理解基点上的差异,是朱熹与张栻对《太极图说》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70]
(二)心性论
向世陵先生认为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71]张栻与朱熹的论辩中,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心性论展开的。成中英先生通过讨论朱熹与张栻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辩,概括了孟子以来心性之学的演变发展,提出了“心之九义”说:心的本体性、活动性、创发性、情感性、知觉性、意志性、实践性、统合性和贯通性。[72]以下将对张栻与朱熹讨论频繁的中和说、仁说等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中和之辩是张栻与朱熹讨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苏铉盛对中和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叙述了从二程经过胡宏到张栻和朱熹等宋代理学之中和说,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察识涵养说之发展脉络和含义。考察了南轩早期中和说即先察识后涵养,与晚期察识与涵养并进的不同观点,及其在思想变化过程中与朱熹的交往情况。[73]
“仁说”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理论构成部分,亦是儒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苏铉盛指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造成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74]向世陵先生则认为张栻不认同“天地以生物为心”,重视“复”在天地生物和德性修养中的价值。天地之心落实为人心,重在将天地之心与人心和仁德统一起来。[75]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76]有关张栻“仁说”的考证,亦是研究其“仁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家星教授就朱子与张栻“仁说”研究中争论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仁说》为南轩本人所作,朱、张“仁说”并无“胜负”之分,二贤在切磋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77]赖尚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做了进一步深入的考证,确定了二人《仁说》的成书时间。[78]两人所作《仁说》时间的确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二人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历程。
(三)工夫论
察识与涵养工夫是张栻中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丽梅对张栻的工夫论做了集中研究,认为张栻的工夫论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不同的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其工夫论正是在与朱子不断地交涉与论辩中逐渐形成的。[79]另外,张琴对张栻的“格物致知”思想亦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在设立性与太极为宇宙与道德本体的前提下,张栻凸显了心的“主宰者”地位,强调“虚灵知觉”之心对于性情的表达与彰显。张栻将格物致知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心与“物”交往、认知与实践的完整过程。由此,他建构了颇具心学特点的“有诸己”的格物论,格物致知的关键并非外于心体的事物与事物之理,而恰恰须落实于此心物交往过程中的心体。[80]
(四)伦理观
伦理道德观是张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张栻涉及伦理的理欲之分、义利之辨以及孝悌观,皆有所研究。邹啸宇指出,义利之辨系南轩理学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关涉其整个学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等重大问题,而其实质也即是理欲之辨。南轩从“意之所向”即行为的动机处,以顺性之“无所为而然”与逆性之“有所为而然”十分精微地辨析义利之分、理欲之别,并且在存天理遏人欲的工夫论上,力主以“反躬”为本,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备受朱子、真西山、杨诚斋等学者的称颂和尊崇,对宋代理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81张栻在义利观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和贡献。粟品孝认为义利观是张栻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精粹,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卓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甚至可以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说相提并论。[82张利明则指出义利观有以下几点现代启示:(1)在经济领域,防止见利忘义;(2)在政治领域,防止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3)在文化领域,防止急功近利,杜绝重利轻义。[83]舒大刚教授从“忠孝传家,世生贤达”,“仁以孝悌为本,孝以爱敬为实”,“政治以励俗为本,劝俗以孝悌为要”等三个方面,初步考察了南轩孝悌观的内容,弥补了南轩孝悌观思想研究之阙。[84]
五、经学思想研究
张栻的经学作品主要有《论语解》《孟子说》以及《南轩易说》这三部。对于张栻经学思想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三部著作上,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到张栻的礼学和诗经学。蔡方鹿教授指出,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85]
(一)四书学
肖永明教授认为张栻对《四书》思想资料非常重视,《四书》是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其本体论、人性论、义利观、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的建构,是与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6]
在张栻的著作中,《论语》最为晚出,代表着他成熟时期的思想,是研究其经学和理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论语解》的解经风格上,肖永明教授认为张栻的《论语解》具有宗奉二程、创造性的阐释以及鲜明的理学色彩等特色。[87]吴亚楠以《论语·学而》的注解为例,对张栻与朱熹的解经理路进行了比较,指出张栻《论语解·学而》具有重理重行的特色,朱熹《论语集解·学而》具有兼采汉宋的特点。[88就《论语解》阐发的具体思想来说,唐明贵认为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读,认为张栻提出了变化气禀之性以复其初的思想、“居敬主一”的工夫论;阐发了相须并进的知行观、义利观。[89]
张栻一直很重视《孟子》的讲授,《孟子说》亦是其后期完成的代表作品。郭美华教授指出,孟子的道德哲学有两个基本概念,即本心(良知)和善。张栻对孟子本心的解释,虽然常有着不彻底性和模糊性,但其以无蔽论本心,从源初自然绽放到强调本心实现自身的整体性与过程性,从心物、心身以及人己关系的统一论本心的实现,到强调善是基于个体力行而自为肯定的实现,彰显了一条拒斥抽象思辨及虚构精神本体而强调力行的理解道路。90德国学者施维礼以张栻《孟子说》中《万章上二》的诠释为例,认为张栻能够把过去历史事件、孟子对此事件的分析、后人的注释以及其他文献的数据做一个合理的统合,这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得以保证的原因所在。[91]
(二)易学
《南轩易说》是张栻易学的代表作,目前所存的版本皆有缺失,杨世文在《张栻集》中对《南轩易说》进行了完整辑佚[92]。对张栻《南轩易说》的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初才陆续出现专门的研究。蔡方鹿指出,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93]在论及《南轩易说》的解经风格时,章启辉认为张栻《南轩易说》于时贤先贤皆有承接,在趋时而主义理易学的同时复归《易传》理路:义理本于占筮,基于象数;在回归《易传》理路的同时又异于朱熹:以象为体,数为用,器为体,道为用,为其学术的经世致用确立易学基础,提供易理依据。[94而对于张栻与朱子在易学解经风格上的不同,杨朗说得更详细。他认为在朱子《本义》中,象数与义理得到了一种综合的处理,并小心翼翼地维持住两者的平衡,朱子要协调好两种不同目视所构造的图景,张栻的《南轩易说》则着意地保持与宋代象数易的距离。[95]
(三)礼学和诗学
张栻在礼学和诗经学方面,并没有成系统的著作,但在文集里边亦有零散的论述,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对于张栻礼学和诗经学的研究,虽不是张栻思想研究的主流,亦有学者对此做了研究。在礼学方面,殷慧从以理论礼、以礼为学、以礼为教等三个层面探讨了张栻的礼学思想。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96在《诗经》研究上,张栻虽无有关研究专著,但其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叶文举认为,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97]对于“学者之诗”,学界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陶俊则主张辨证看待“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98]
六、实学与教育思想研究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倡导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反对“空言”的实学思想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振纲和邢靖懿认为,张栻注重把性理哲学与经世致用、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故避免了流于空谈义理、空疏无用的弊端。张栻经世致用的学风,泽被后世,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近千年,至今广为流传。[99]
(一)异端观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时代大背景下,张栻对待佛教持极力排斥态度。正是对佛老等异端的批判,张栻提出了经世致用和求实求理的实学思想。李承贵认为张栻对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主要表现为:对涉佛、嗜佛、传佛的儒家之批评,对佛教某些教理教义之批判,提出“反经”“固本”以消除佛教观影响之策略等三方面内容。[100]刘学智指出,张栻从儒佛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片面性和对佛教理论了解不够深入的思想弱点。[101]蔡方鹿和胡长海对张栻的“异端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辞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102]
(二)社会政治思想
作为一位理学家、政治家,张栻在继承儒家政治思想以及积累的许多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治道、治术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治国理政主张。邹啸宇从体用的角度考察了张栻的经世思想,阐明其政治哲学建构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有三:内圣与外王相倚相成的内圣外王关系;“仁心为体,仁政为用”的为政理念;“体用兼备,本末具举”的为政之方。[103]张建坤则认为张栻从天道推衍人道的生民政治理路,其内涵包括“立君为民”“君臣共治”和“养民教民”三个层次,三者共同构成了君—官—民和谐一体的理想社会政治图景。[104]蔡方鹿先生近年对来张栻理学思想的社会价值研究,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105]经世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包含着的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以骄矜为乐”的享乐主义、“从事于奢靡”的“四风”加以反对的思想,即使对现代社会纠正不良风气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106]
(三)教育思想
对于张栻的教育思想研究,目前最新成果是张建东《传道济民: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一书。该书是从史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写作的第一部专门研究张栻教育思想、教育贡献的著作,填补了张栻教育思想研究的若干空白。张建东以张栻的“传道”“济民”等活动和事迹为中心,充分借鉴社会史、生活史、身体史、心态史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深切关注到张栻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家庭生活及社会交往状况等诸多方面,对张栻波澜壮阔的一生做了立体、全景式考察,以更为完整的研究维度逼近历史之真,开拓了教育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范式。107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并创办了城南书院。他以书院为基地,教授与传播理学思想,因此书院教育亦是张栻教育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刘刚认为张栻力推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以外,另一层意义在于抗衡与回应泛滥于当时社会的佛老二氏之学、王安石新学及当时争驰于功利之末的世俗之学。张栻从通经明理、修身成德、经世致用为旨归的理学立场,将佛老二氏之学、王安石新学与重利忘义的世俗治学之风,在不同程度上皆视为“俗学”;并从人性论、心性论语知行观理论出发,对当时“俗学”进行强烈批评与坚决抵制,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反俗学思想。[108]
七、回顾与展望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栻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从思想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研究的视角等方面,皆有进步和深入的空间。笔者认为,今后张栻思想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第一,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勘误方面。资料的完整、翔实与真实,是我们展开研究的基础。首先针对张栻的文集来说,现在仍有许多逸文,比如据苏费翔推测,至少在《朱子语类》、蔡节《论语集说》以及《西山读书记·乙部》等书中还有不少逸文可寻。[109]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逸文,完善张栻的研究材料,一直是我们需要努力之地。另外就文集而言,张栻著作流传版本众多,文字上多有存在差异的地方,易造成解读上的差异。因此对张栻著作进行翔实校勘,整理出一个最能真实反映出张栻思想的版本,很有必要。
第二,关于张栻生平和影响的研究。张栻的年谱可进一步考证、完善和编年,虽然现存有三部张栻年谱,但总体而言,都极为简略,多语焉不详。在现代学者对张栻材料进行了进一步整理和考证后,如书信编年,诗歌编年和涉及人物考证等,可尝试重新编写张栻年谱,进行《张栻年谱长编》,以期能更详尽地展示张栻的生平事迹,并展现其时代的特点、家族系谱、交友状况以及学术思想变化等。其次,张栻思想对海外思想家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张栻交游情况研究。《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信汇编》一书的出版,对于学者研究张栻与同时代的学者交游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有待学者进一步挖掘张栻书信交往中的思想和观点。张栻与其他学者或其他学派,比如与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人之间互动,对蜀学、闽学的影响等,皆可进一步展开。虽然目前对张栻交游的研究,多集中于张栻与朱熹之间,但两者间的学术论辩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就整体性研究而言,目前仍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张栻与朱熹学术论辩方面的专著。另外从研究角度来说,目前对张栻的相关研究,多半集中在张、朱之间对于几个重要理学议题的讨论上,比如中和之说、胡子知言疑义、仁说以及太极说等。这些议题虽在现代学者的努力下,多有成果,但却往往是从朱熹的角度切入,反观就张栻来谈张栻,站在张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朱子之学,对比之下少之又少。换个角度出发,从另外一个视野审视朱子与张栻的交游,一定会有不同于现在研究的新收获。从二者研究的切入点来说,以往大多以中和、仁说等理学命题讨论的形式来展开,然而经典是思想诠释的基础,从具体的经典与经典之间的比较出发,对南轩与朱子的经典著作的诠释风格,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等方面的异同,通过这种比较,如何正确定位二人之间的关系等,皆是我们可以努力展开的研究方向。
第四,张栻思想的重新诠释。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物思想的诠释,亦应与时俱进。有关张栻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距今已过去20多年,这20多年对于张栻思想的研究,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视野以及研究材料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在新视野、新方法以及新材料的支撑下,充分吸取海内外先进研究成果,深入其义理系统内部,展开深入的、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探讨,由此对张栻思想重新进行诠释,是时代对我们发出的要求。其次,抛开哲学思想之外,将张栻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结合起来,从他的心路历程来全新看待张栻变化与发展的一生,给予他全新的定位,也是很有必要的,据此编写类似于《张栻传》等相关的传记,使张栻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张栻研究朝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附注
注释:
[1]为了避免因笔者的误读,而扭曲了作者的本意,故摘要之方式尽可能使用作者原有的论述说明,而不加上笔者自身的诠释于其中。
注释:
[1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18.
注释:
[1 J爱知学院大学准教授,筑波大学大学院文学博士,著有《朱子学の普遍と東 アジア》(ペりカ、ん社,2011年)。
[2]原题《朱子学から考える権利の思想》,ペりカ、ん社,2017年6月。
[3]《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注:“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4]中嶋谅氏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人文科学专攻博士课程,现任学习院大学客员研究员。著有《陸九淵と陳亮》(早稻田大学モノグラフ, 2015 年)。
[5 ]原题《陸学の“人心” “道心”論——いわゆる“朱陸折衷”の淵源を辿る》,载《言語文化社会》第15号,2017年3月,第31〜52页。另,论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https://glimre.repo.nii.ac.j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 action= 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 detail&item_id=3629&item_no= 1 &page_ id=l 3&block_ id=21
[6]参考石田和夫氏,《銭融堂について陸学伝承の一形態》,《中国哲学论集》2,1976年。在该文中,石田氏指出,朱陆折衷的倾向是继承了陆学初传的舒璘 和袁燮,往前追溯的话则是试图调停朱陆的吕祖谦。
[7]早坂俊广氏《朱熹の“人心・道心”論(一)“人心・道心”解釈の展開について》(《哲学》43,1994年10月),将朱子的“人心”“道心”解释的变迁 分作四组加以讨论。
[8]林文孝,立教大学文学部文学科文艺•思想专修教授。
[9]原题《“仁と為す”か“仁を為す”カ、:朱熹〈論語集注〉のもとでの〈論語〉顔淵篇“克己復礼為仁”の訓読》,载《境界を越えて:比較文明学の 現在》,第17号,2017年2月,第31〜49页。
[10]中村惕斋(1629〜1703)《論語講義》(《先哲遺著•漢籍国字解全書》所收)、松川健二《“克己復礼”解釈史研究》、宇野哲人(I)《〈集注〉による〈論語〉通釈(11)》、佐野公治《“克己復礼”解釈史研究》、倉石武四郎《〈集注〉による〈論語〉翻訳》、土田健次郎译注《論語集注》(2013年、 平凡社)、吹野安•石本道明《〈孔子全書〉での〈集注〉引用》。
[11 ]木南卓一《〈集注〉詳解》。宇野哲人(II)《集注》的训读翻译,经文训作 “仁と為す”、朱注训作’’仁と為す”。
[12]“‘克己复礼为仁’,与’可以为仁矣’之’为',如‘谓之‘相似;与’孝弟为仁之本‘,’为仁由己'之‘为'不同。”(《朱子语类》卷四一,10条,甘节录)“'人之为道而远人',如'为仁由己'之'为','不可以为道',如 '克己复礼为仁'之'为'。”(《朱子语类》卷六三,94条,李阂祖录)
[13]“问:'克己复礼为仁',这'为'字,便与子路'为仁'之'为'字同否。 曰:然。又问:程先生云'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恐'是仁’字与’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个,便是这个。盖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复ネし'所以为仁也。仁是地头,’克己复礼'是工夫,所以到那地头底。”(《朱子语类》卷四一,61条,吕春录)
[14]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 助教。
[15I原题《陳亮の“事功思想”とその孟子解釈》,《集刊东洋学》116号,中国 文史哲研究会,2017年1月。
[16]《陈亮集》卷二八《癸卯书》“故曰,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 而无常废。”
[17]《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第八书“来书心无常泯、法无常废一段,乃一书之关键。……固无常泯常废之理,但谓之无常泯,即是有时而泯矣。 谓之无常废,即是有時而废矣。”
[18I《陈亮集》卷二八《又乙巳秋书》:“亮大意以为本领阂阔,工夫至到,便做 得三代。有本領无工夫,只做得汉唐。”
[19]《陈亮集》卷九《勉强行道大有功》:“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 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
[20]《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 何有。’”
注释:
[1 ] JeeLoo Liu, Neo-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Mind and Moralit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
[2 ] Hoyt Cleveland Tillma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Student Opinions on the Modernized Zhu Confucian Wedding,n in Shing Muller and Armin Selbitschka, ed., Uber den Alltag hinaus: Festschrift fur Thomas 〇, Hollmann zum 65. Geburtsta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pp.34]〜352.
[3 ] Margaret Mih Tillman and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 Joyful Un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Zhu Xi Family Wedding Ceremony,n Oriens Extremus 49, 2010, pp.115 〜I42.
[4 ] Eiho Baba, "Zhijue as Appreciation and Realization in Zhu Xi: An Examination through Hun and Po,"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7.1, 2017, pp.301 〜317.
[5 ] Larson Di Fiori, Henry Rosemont, uSeeking Ren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7.1, 2017, pp.96 〜]]6.
[6 ] Courtney R. Fu, uLiterat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The Quanzhou Community of Lea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7.
[7 ] Zhang Yunshuang, uPorous Privacy: The Literati Studio and Spatiality in Song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7.
注释:
[1]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95页。
[2]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刘再华,《晚清时期的文学与经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4页。
[4]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1700页。
[5]刘毓庆,《<诗>学之“兴”的还原与背离》,《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6]傅斯年,《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新潮》,1919年第1卷第4期。
[7]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8]周予同,《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65~66页。
[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11页。
[10]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1272页。
[11]谢谦,《朱熹“淫诗”之说平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2]赵沛霖,《试论<诗经>情诗的历史命运》,《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吴正岚,《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谢海林、周泉根,《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3]姜龙翔,《朱子“淫奔诗”篇章界定再探》,《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2年第12期。
[14]黄景进,《朱熹的诗论》,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1177页。
[15]〔美〕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16]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7]汪大白,《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孔子研究》,2002年第3期。
[18]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4页。
[19]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7页。
[20]蔡方鹿,《朱熹<诗经>学析论》,《经学研究论丛》第七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
[21]郝永,《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4~225页。
[22]陈昭瑛,《朱熹的<诗集传>与儒家的文学社会学》,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203页。
[23]邹其昌,《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4]曹海东,《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9页。
[25]郝永,《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26]陈志信,《诗境想象、辞气讽咏与性情涵濡——<诗集传>展示的诗歌诠释进路》,《汉学研究》,2011年第29卷第1期。
[27]戴志钧,《朱熹在楚辞研究中的开拓性贡献》,《文史哲》,1990年第3期。
[28]杜海军,《幽忧穷蹙怨慕凄凉——论朱熹的楚辞鉴赏观》,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八百七十周年、逝世八百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29]〔韩〕朴永焕,《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天府新论》,1995年第4期。
[30]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48、1054页。
[31]孙光,《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章句)<补注><集注>比较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页。
[32]罗敏中,《以儒注屈融屈于儒——论朱熹的尊屈倾向之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3]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34]何新文、徐三桥,《论洪迈与朱熹对<高唐<>神女赋>评价的差异——兼及宋玉辞赋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把握》,《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
[35]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36]于浴贤,《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徐涓,《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江淮论坛》,2014年第3期;梁升勋,《朱子<楚辞集注>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5年。
[37]肖伟光,《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云梦学刊》,2014年第3期。
[38]徐涓、王国良,《朱熹格物致知与楚辞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39]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页。
[40]吴长庚,《朱熹文学研究之三大著述》,《上饶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41]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1745~1746页。
[42]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42页。
[43]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44]王哲平,《朱熹文学思想论略》,《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45]李春强,《朱熹<论语集注>文学观简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6]张立文,《<朱熹文学思想论>序》,《上饶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47]杨儒宾,《战后台湾的朱子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2000年总第76期。
[48]周予同,《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81页。
[49]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陈千帆全集》(第十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6页;张健,《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8~12页。
[50]﹝日﹞横山伊势雄,《论朱熹的文学哲学一体观》,徐中玉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3页。
[51]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61页。
[52]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114页;吴法源,《试论朱熹的文道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3]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3页。
[54]程刚,《宋代的太极观与文学本原论》,《周易研究》,2014年第4期。
[55]郭绍虞,《朱子之文学批评》,《文学年报》,1938年第4期。
[56]胡明,《关于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57]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58]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8~259页。
[59]石明庆,《论朱熹理学与诗学之关系》,《朱子学刊》(第十五辑),2005年,第15页。
[60]黄景进,《朱熹的诗论》,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1177页。
[61]丁放、孟二冬,《试论宋代理学家的诗学理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62]何寄澎,《朱子的文论》,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1213页。
[63]闵泽平,《朱熹文章观论略》,《朱子学刊》,2008年第1辑,第117页。
[64]踪凡,《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方铭、李诚编,《中国楚辞学》(第十二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65]全华凌,《论朱熹的韩愈研究》,《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
[66]黄炳辉,《晦庵评唐诗辨》,邹永贤主编,《朱熹思想丛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67]莫砺锋,《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68]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69]谢谦,《朱熹文学批评的批评》,《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70]周予同,《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83~84页。
[71]胡明,《关于朱熹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72]郭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73]许总,《论南宋理学极盛与宋诗中兴的关联》,《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74]莫砺锋,《理学家的诗情——论朱熹诗的主题特征》,《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
[75]李育富,《朱熹易学思想与诗歌关系考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76]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41页。
[77]〔美〕陈荣捷,《论朱子<观书有感>诗》,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11页。
[78]﹝韩﹞李秀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
[79]﹝日﹞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1页。
[80]石明庆,《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81]朱杰人,《朱子诗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82]胡迎建,《朱熹诗词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83]饶宗颐,《唐宋八家朱熹宜占一席论》,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第1157页。
[84]莫砺锋,《论朱熹的散文创作》,《阴山学刊》,2000年第1期。
[85]闵泽平,《朱熹文章风格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86]方笑一,《论朱熹经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87]王仕强,《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8]黄拔荆、周旻,《论朱熹的词》,邹永贤主编,《朱熹思想丛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89]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注释:
[1]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下册卷29《与张定叟侍郎》,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2页。
[2]〔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3]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1页。
[4]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70页。
[5]蔡方鹿主编,《张〕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前言。
[6]〔日〕高畑常信著,《宋代湖南学の研究》,东京:秋山书店,1996年。
[7]蔡慧清,《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353页。
[9]蔡方鹿,《张拭研究简述》,《哲学动态》,1992年第3期。
[10]蔡方鹿,《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
[11]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2]苏铉盛,《张栻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3]王丽梅,《张栻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4]邢靖懿,《张栻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5]吴亚楠,《张栻经学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17]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18]胡杰、冯和一,《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
[19]张拭著,杨世文点校,《张拭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20]王开琸、胡宗楙、〔日〕高畑常信著,邓洪波辑校,《张栻年谱》,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21]任仁仁、顾宏义编撰,《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22]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九,《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130~4141页。
[23]邓洪波辑校,《张栻年谱》,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24]胡昭曦,《论张栻的学术源流》,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5~189页。
[25]周建刚,《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求索》,2016年第11期。
[26]郭齐,《胡宏性本体论对张栻的影响》,《船山学刊》,2014年第1期。
[27]钟雅琼,《张栻对胡宏思想的传承及调整》,《孔子研究》,2014年第3期。
[28]金生杨,《张栻对张浚学术的继承与扬弃》,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0~509页。
[29]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8页。
[30]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31]夏君虞,《宋学概要民国沪上出版书·复制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07页。
[32]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98页。
[33]胡昭曦,《南宋二江诸儒与南轩之学返传回蜀》,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75页。
[34]黄家羲原著,全组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09页。
[3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十九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36]同上注,第350页。
[37]蔡方鹿,《张栻与宋代理学》,《船山学报》,1988年第2期。
[3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354页。
[39]蔡仁厚,《宋明理学·南宋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6页。
[40]曾亦,《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41]李可心,《由心的出入问题反思张栻之学的式微》,《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
[42]〔韩〕이영호,《南轩学의수용을통해본寒冈学의새로운이해》,《대동한문학》,2017年第50辑。(李英镐,《吸收南轩学而产生之寒冈学的新理解——以寒冈郑逑的论语学为中心》,《大东汉文学》)[43]〔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90页。
[44]〔美〕田浩,《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45]任仁仁、顾宏义编撰,《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46]杨世文,《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1~227页。
[47]杨世文,《读<南轩集>札记》,蜀学研究中心主办《蜀学》第8辑,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67~82页。
[48]〔日〕山口察常,《朱子と张南轩》,《大崎学报》,1938年第92期。
[49]陈代湘,《朱熹与张拭的学术交往及相互影响》,《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第82~87页。
[50]肖永明,《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1]李清良、张洪志,《“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2]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1~139页。
[53]陈代湘,《朱熹与张拭的思想异同》,《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54]〔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90页。
[55]〔美〕田浩,《朱熹与张〕、吕祖谦互动述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6]潘富恩,《论“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57]〔日〕高畑常信,《朱子·张南轩·吕祖玄の理学思想の相违》,《东京学芸大学纪要·第2部门》(人文科学),1996年第47集,第133~151页。
[58]刘玉民,《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以吕祖谦书信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59]钟琼雅,《张栻与蜀地学者交游考述》,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3~436页。
[60]邹锦良,《“知行”之辩:周必大与张栻的学术交谊考论》,《孔子研究》,2013年第4期。
[61]张琴,《论张栻理学体系的逻辑结构》,《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
[62]郭齐,《张栻学术的几个特点》,徐希平主编,《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63]陈谷嘉,《论张栻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兼论湖湘学派理学思想的特色》,《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64]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65]苏铉盛,《张《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66]〔德〕苏费翔,《张栻<太极解义>与<西山读书记>所存逸文》,收入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9~210页。
[67]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05~1611页。
[68]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72~403页。
[69]吴亚楠,《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2期。
[70]李丽珠,《“喜合恶离”与“形名太过”——朱熹注解〈太极图说〉〈通书〉过程中与师友互动之分析》,《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
[71]向世陵,《张栻的“性善”论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72]〔美〕成中英,《朱熹与张拭的论学:性体情用心统与性体心用导向心之九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73]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4~431页。
[74]苏铉盛,《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辩》,《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75]向世陵,《张栻的仁说及仁与爱之辨》,《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76]向世陵,《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文史哲》,2018年第1期。
[77]许家星,《朱子、张栻“仁说”辨析》,《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4期。
[78]赖尚清,《朱子与张拭“〈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79]王丽梅,《张栻早期工夫论考》,《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1期;王丽梅,《“己丑之悟”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求索》,2006年第4期;王丽梅,《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张栻与朱熹交涉论辩管窥》,《孔子研究》,2006年第4期。
[80]张琴,《张栻“格物致知”思想探析——落实于心体的格物论与察识涵养并进之工夫论》,董平主编,《浙东学术》第3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86页。
[81]邹啸宇,《天理人欲不并立,反躬以存理遏欲——南轩理欲论探析》,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0~343页。
[82]粟品孝,《“论说”与“事业”:理解张栻义利观的两个维度》,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51~57页。
[83]张利明,《“无所为”与“有所为”——张栻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刍议》,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1~319页。
[84]舒大刚,《忠孝传家:南轩“孝悌观”初探》,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7~181页。
[85]蔡方鹿,《张栻经学探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86]肖永明,《张拭之学与〈四书〉》,《船山学刊》,2002年第3期。
[87]肖永明,《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88]向世陵主编,《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理学体贴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0~228页。
[89]唐明贵,《张栻〈论语解〉的理学特色》,《哲学动态》,2010年第8期。
[90]郭美华,《无蔽之心与善的意蕴——论张拭〈癸巳孟子说〉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91]〔德〕施维礼(WolfgangSchwabe),《诠释与传承——以张栻〈孟子说〉中对〈万章上二〉的注释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传承》,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6~310页。
[92]对《南轩易说》的考证,参见金生杨,《张★〈南轩易说〉考辨》,蔡方鹿、舒大刚主编,《儒家德治思想探讨》,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593~603页,以及吴亚楠,《张栻经学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3]蔡方鹿,《张栻易学之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6期。
[94]章启辉,《〈南轩易说〉象数说述评》,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5~396页。
[95]杨朗,《〈南轩易说〉中的目视——以卦序问题为中心》,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拭、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14~122页。
[96]殷慧、郭超,《传道、济民、修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97]叶文举,《张拭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
[98]陶俊,《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99]李振纲、邢靖懿,《张栻内圣外王合一的经世之学》,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5~143页。
[100]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10~237页。
[101]刘学智,《张拭“儒佛之辨”刍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02]蔡方鹿、胡长海,《张拭“异端”观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03]邹啸宇,《“体用相须,贵体重用”——论张拭政治哲学建构的基本理念》,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91~202页。
[104]张建坤,《“生民”与“民生”——张栻政治思想发微》,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229~248页。
[105]蔡方鹿,《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探讨》,《船山学刊》,2014年第1期。
[106]蔡方鹿,《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周景耀主编,《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44~50页。
[107]张建东著,《传道济民:名于一世的教育家张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08]刘刚,《张拭反俗学思想初论——从其书院教育思想说起》,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2~373页。
[109]〔德〕苏费翔,《张拭〈太极解义〉与〈西山读书记〉所存逸文》,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9辑),第210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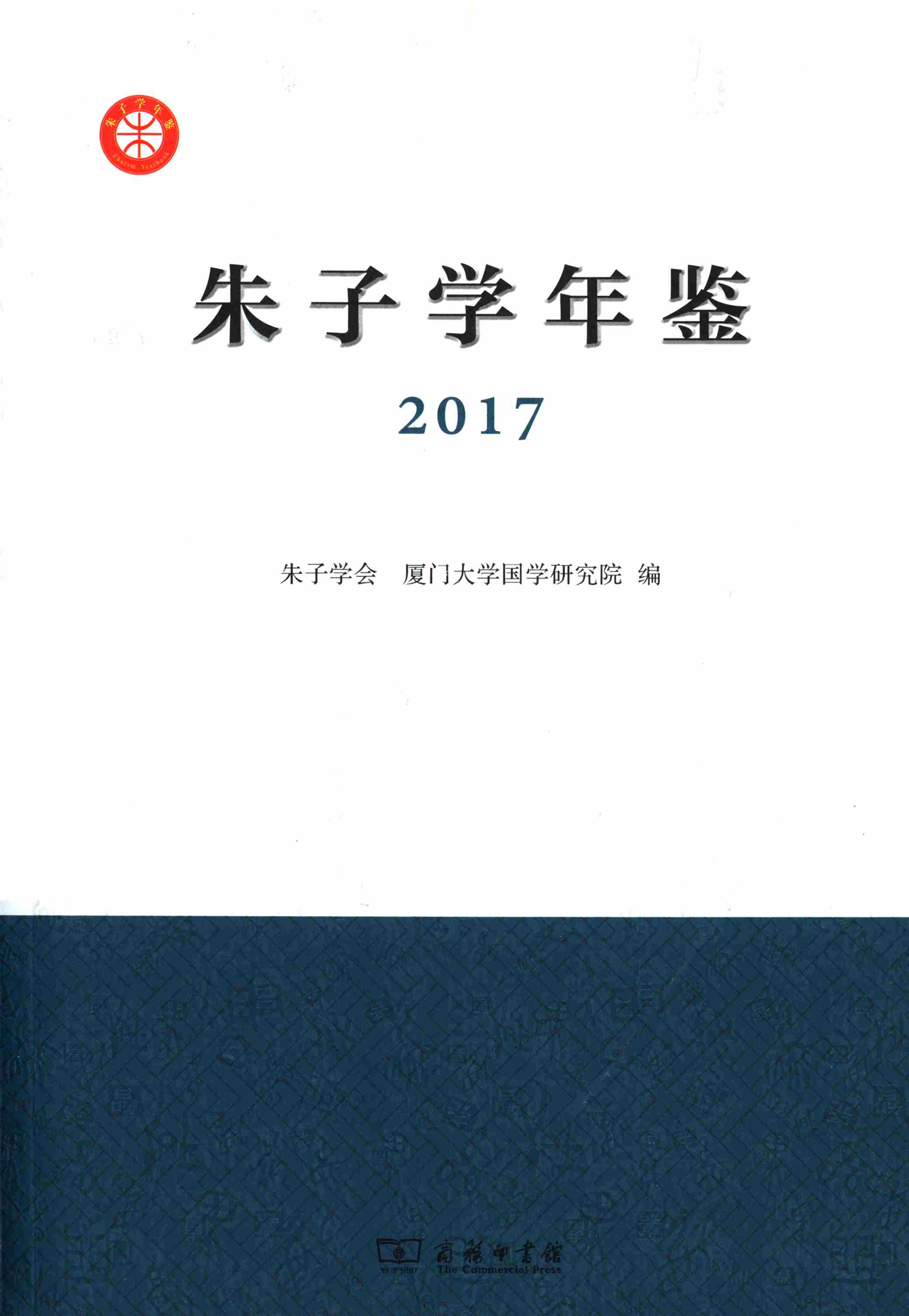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7》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仁者人也”新解》《朱子学的构建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朱熹与陈亮往来书信编年考证》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