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新仁学的建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7》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109 |
| 颗粒名称: | 宋儒新仁学的建构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5 |
| 页码: | 070-08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孔子对于“仁”的内涵的确立以及其在道德主体性精神中的作用。为了使这种主体性仁学成为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德法则,需要解决人道与天道合一的理论构建。宋儒通过重新构建经典体系和重新诠释仁学,建立了一种天人合一、体用圆融的新仁学。这不仅是一种哲学构建,也是一种天人合一信仰的重建。文章还提出了问题,宋儒是如何完成对儒家仁学的诠释和建构的,以及宋明儒家新仁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
| 关键词: | 理论建构 宋儒 经典体系 |
内容
孔子坚持从人的道德主体性精神中,确立了“仁”的价值内涵。但是,这一种主体性仁学要成为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必须解决人道与天道合一的理论建构。
宋儒通过重建“四书”的经典体系和重新诠释仁学,建构出一种天人合一、体用圆融的新仁学。这既是一种体用合一的哲学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信仰重建。宋儒如何完成儒家仁学的诠释与建构?宋明儒家新仁学的建构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何意义?
一、仁学的主体精神与形上依据
为了维护三代先王创造的礼乐文明,孔子创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从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意志的基本精神性要素,确立“仁”的基本内涵。经过孔子的仁学思想,作为三代文明核心的“礼”就不再是事神致福的手段,而是人心之“仁”的外在表达,体现出人的情感、理性、意志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说,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在人性以及人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意志的精神要素中,找到了“六经”之礼的人本依据。
孔子信奉、实践主体性精神的仁,必然面临主体精神的外在依据问题。孔子倡导为仁之道首先依赖于君子的自觉追求,但是仁道的外在实现还可能依赖于天命。他曾发出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孔子曾多次讲到“天”“天命”的主宰性力量,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畏天命。”[3]“天”是绝对不能获罪的,君子在“天命”面前必须保持敬畏、虔诚的态度,就是因为“天”“天命”对主体精神有强力的约束。所以,孔子不仅主张“畏天命”,同时也倡导“知天命”,他相信这一种具有主宰力量的“天”“天命”,应该是理性化的认知对象。可见,孔子的“仁”虽然能够确立“礼”的内在依据,但是,作为人的主体性精神的“仁”,如果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为准则和客观性社会现实,就必须表达出形而上的主宰力量。一切具有为仁的情感、理性、意志的人,必须要寻找、信仰一个外在的超越依据和最高主宰。
孔子后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人格精神与宇宙天道之间的联系,早期儒学的许多重要典籍如《子思子》《孟子》《易传》,也在思考和探讨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那些受到宋代儒家重视的早期儒家典籍,其实均是在探索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儒家诸子学的著作,儒家诸子试图为孔子的主体精神的仁心确立天道依据。
早期儒家探索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两种。
其一,从人道到天道,即从人的内在仁心领悟、提升出一种普遍性、崇高性的天道。《子思子》《孟子》论述了仁道的人性依据和最高主宰“天”的关系。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4]
在孟子那里,“天”“天命”主要是作为仁心、仁性的外在依据。那么,究竟什么是“天”“天命”呢?从《中庸》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天”“天命”是从主体性精神中提升起来的一种普遍性、崇高性的超越存在。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5]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6]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
这些论述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早期儒学努力探索仁之心性(人道)与天道之间的联系与特点。儒家思孟学派所讲的“天”“天道”既不是一种自然宇宙论,也不是一种宗教创世论,而是与人的情感、理性、意志的道德精神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存在,是一种希望通过主体性道德追求而提升出来的精神崇高性、价值普遍性。在《中庸》的思想中,“天道”无非是通过修炼而达到的“诚”的崇高人格,是一种“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精神境界。思孟学派肯定仁心、仁性是人的普遍性、崇高性特质,故而“天命之谓性”主要是强化仁心的精神崇高性、价值普遍性,以确立一种人文精神的信仰力量。
其二,从天道到人道,即从外在的自然天道论推导出仁义道德。《易传》是早期儒家探寻自然天道的哲学著作,它十分关心对宇宙自然之道的思考。《易传》在论述宇宙天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人道的要求。《易传·系辞》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易传·系辞》所描绘的宇宙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故而他们将“生”作为“天地之大德”。能够与“天地之大德”“生”相配的是圣人之“仁”,显然,他们认为人的“仁”之德与天的“生”之德具有相通的共性。由于《易传》旨在建构一个自然宇宙论,“生”才是“天地之大德”,“仁”不过是对“生”的仿效、追随。所以,《易传·系辞》总是将“仁”纳入到对“天地之大德”的仿效、追随:“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原来,“仁爱”只不过是伟大天道的显现与功用(“显诸仁,藏诸用”),是“与天地相似”“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具体表现。总之,《易传·系辞》是通过自然天道论来证明仁义的人道论。
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探索了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当然,他们的论证还存在一些不足。思孟学派是由人到天,《易传》是由天到人,但是这两种思想观念有什么关联,先秦儒家没有将两个不同理论体系打通,仁道论与天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他们的天道论、人道论显得太粗略,还不是精深的哲学化形上思辨。
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8]
董仲舒所论述的“仁”,完全是与人的心、志、气、欲等涉及人的情感欲望、精神意志等方面的因素有关,这正是对早期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他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关于仁之爱的观念,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强调:“故仁者所爱人类也。”[9]这一种“爱人类”的“博爱”思想,是传承孔子的仁学思想。
但是,另一方面,汉儒在关于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方面,则是继承三代时期天神上帝的宗教信仰。董仲舒比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仁与天神的关系,他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10]在董仲舒看来,人所具有的仁的情感与意志,其实是来源于“天”所具有的仁的情感与意志。而且,董仲舒吸收了西周时期“以德配天”思想,他所说的“天”完全是神灵之天。他认为“天”是具有仁的情感意志的“百神之大君”,人格神的“天”可以通过各种灾异向人类表达他的情感与意志,即所谓“谴告”。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宗教思想来建立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显然是继承了三代时期天神上帝信仰的体系,这与儒家的人文理性精神是不一致的。
二、北宋诸儒的新仁学
两宋儒家学者自觉承担“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在面临佛、道两教的严重挑战时,一方面回归儒家经典,努力恢复儒家仁学的人文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创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推动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宋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仁学,通过对仁学的创造性诠释,进一步确立仁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北宋是理学的奠基时代,北宋理学家也是新仁学的奠基人。宋儒建构新仁学固然与佛教的心性论、道家道教的宇宙论的挑战有关,但是新仁学的学术资源却是依据于先秦儒家经典。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典《易传》“四书”的创造性诠释,论证天道与人道结合的新仁学。“北宋五子”对新仁学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从《周易》的宇宙天道论仁学引申出“四书”的人道论仁学,实现了《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的结合。其二,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体用之辨”的诠释方法,对“四书”的人道仁学做出形上层面的本体论诠释,大大提升了仁学的哲学意义和精神信仰意义。
首先,我们探讨“北宋五子”新仁学的第一个贡献,考察他们如何从《周易》的自然主义天道论出发,引申出“四书”的人道主义仁学,建构出一种天道和人道一体化的新仁学。
本来,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两大类形而上学,一类是宇宙论的形而上学,一类是自我论的形而上学。而宋儒在重新建构新仁学时,则坚持将“宇宙论”与“自我论”两种形而上学统一起来,具体而言,就是将《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结合起来。他们既发挥《周易》的宇宙论思想资源,从而建构更具自然主义色彩的天道仁学;又通过诠释“四书”的心性仁学,从人的内在仁心提升出一个形而上的依据。而且,宋儒通过大量引入《易传》的思想资源,对“四书”仁学的创造性诠释,将思孟学派的心性仁学与《周易》的天道仁学结合起来,最终建构出一种天道和人道一体的新仁学。
周敦颐是理学奠基人,他的代表著作《太极图说》《通书》,均是将《周易》的宇宙论引申出仁义论的开创性著作。他的《太极图说》论述了太极的宇宙化生到圣人“立人极”的仁义道德的完成过程。周子《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原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原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11]这一个宇宙论哲学源于先秦、两汉的易学,但是,周敦颐的重要贡献是将《周易》的宇宙论与“四书”的仁义论结合起来,“四书”的仁义道德成为这个宇宙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仁义、主静是“立人极”的人道,它们与“无极而太极”的天道是相通的。周敦颐的经典依据主要是易学,他努力将《周易》的宇宙论与“四书”的仁义论结合起来,恰恰体现了从天道到人道的仁学思想特色。
张载从《易》学中引进了“气”的概念,他经过一番学术探索和思想整理,建立起“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他力图在“天人一气”的自然宇宙论基础之上,为儒家仁学思想做出宇宙本体论的论证。张载由天道自然到人道仁爱,大大拓展了儒家的哲学思想。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思想,这一仁爱思想的哲学基础却是“天人一气”的天道论。张载在论述仁者爱人的人道论时,处处表现出乾父坤母、天人一气的天道精神;同样,他在论述“乾坤”“天地之塞”“天地之帅”的天道原理时,其落脚点则是充满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张载在《西铭》中论述为仁之道的人道精神时,无处不在地透露出这一种人道意识与天人一气的天道意识的密切关联。他写道: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12]
张载在《西铭》中表达出一种对普遍性和永恒性仁爱精神的追求,尽管《西铭》中的仁爱精神是建立在宋代士大夫的主体精神与自我存在基础之上的,但是,“吾”之所以能够达到“仁之体”的心理状况和精神境界,完全源于天人一气的天道宇宙论。一个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仁爱精神的人,一定是能够具有、体认到天人一气的天道宇宙论的人。
二程也是从《周易》的宇宙论出发,将《周易》的天理论与“四书”的仁义思想结合起来,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理”成为一个存在于自然、社会中一切具体事物的普遍法则,更为重要的是,理不仅存在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之中,而且支配、主宰着世界的秩序和变化,故而,“理”又成为一个普遍、永恒的主宰者。从其主宰的绝对性而言,它又可以称之为“天”,他们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13]程颐还用“理一分殊”的新观点,来阐明“天理”在宇宙间的统一性问题。二程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乃至鬼神变化都依据于一个统一的天理。但是,天地之间的事物是各有重要区别的,君臣父子因尊卑长幼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事事物物各有其不同的道理。二程通过上述的学说论证,确立了一种以“天理”为中心的宇宙论,将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
其二,“北宋五子”新仁学还有第二个贡献,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体用之辨”的诠释方法,对“四书”的心性仁学做出本体论诠释,将“四书”的心性仁学上升到形而上之道,大大丰富了仁学的哲学意义。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有两种,一种是以汉儒为代表的天人同构、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一种是以宋儒为代表的体用之辨、同体异用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两宋时期,体用之辨成为宋儒诠释儒家经典的一个具有深刻哲学内涵和普遍意义的方法。宋儒通过诠释经典而为儒家的心性伦理建构起形而上的本体论思想体系,其建构本体论的基本方法就是体用论。宋儒通过一系列本体论的诠释后,仁学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仁学所表达的意思是十分世俗而实用的,但是经过宋儒的诠释,这些人伦日用的仁学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仁作为自然情感、交往理性、德性意志而有了形而上的升华,人道之体用就是天道之体用,人作为主体性的情感、理性、意志,最终可以与大本大源的天道、天理相通。
宋儒不满意汉儒以“天人感应”来建立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他们重新回归到人的情感、理性、意志等精神要素,进一步确立“仁”的人道价值和意义。宋儒强调回归先秦儒学,因为从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之所以必须有仁爱的情感,并不是因为“人之受命于天也”,而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内在需求和心性呈现。所以,宋儒希望回归“四书”经典,从人的道德主体精神中追溯“仁”的源头。在宋儒许多经典论著和命题中,“仁”的依据总是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精神的“我”“己”“吾”。宋儒新仁学从人道到天道的哲学建构,首先是在吸收先秦思孟学派心性仁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宋儒在回归孔子以人的主体精神论仁的基础上,重新将仁归之于人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意志的精神心理要素。
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提升主体存在的形而上意义和价值,确立了主体之“仁”的天道意义和依据。宋儒在继承思孟学派心性仁学的基础上,努力从人的内在仁心提升出一个超越性的依据。他们特别关注《中庸》《孟子》,因为思孟学派的仁学是以心性论为基础的。宋儒通过对“四书”心性仁学的创造性诠释,最终使人道之“仁”与天道之“理”结合起来,完成了仁的形上哲学的建构。宋儒在确立仁的形上意义时,反复讲到“仁之体”,即是将作为主体道德精神的“仁”提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体”。程颢认为《西铭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14,意指张载在《西铭篇》中表达出的仁爱精神就是一种普遍和永恒意义的“体”。但是,我们会发现,程颢所讲的“仁之体”,并不是一种外在天地自然或宇宙世界的形而上之“体”,而首先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形而上之体,是以个体意识为基础的内在主体精神的“体”。
我们进一步来考察程颢对“仁之体”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程颢运用“体用之辨”的诠释方法对仁学做出本体论诠释。程颢在一篇专门讨论仁学的文章中说道: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比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在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15]
在这一段话中,程颢首先强调主体的“识仁”,“仁者”是一种“浑然与物同体”的心理状况和精神境界。可见,对宋儒来说,“仁体”首先是一种主体性存在,“识仁”也就是主体通过自己的直觉、体悟,获得对人、物的形而上之本体存在的直觉、境界。程颢的“识仁”,不是一种心之外的“防检”,更非心之外的“穷索”,而是对自己内在之心的察识,直接意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体悟到吾心之仁乃天地之仁,天地之仁亦吾心之仁。
由于宋儒对仁学采用了“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就更进一步融合了《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创建了一种本体论意义的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新仁学。程颢之所以相信仁者可以达到一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是因为这一种精神境界有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前提,即天和人背后有一个相通的形而上意义的“体”。程颢等理学家认为,这一个“体”就是《易传》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具有超越社会功利、道德价值的形上意义。程颢在建构新仁学时,肯定这一个具有“生”的本体贯串于天道和人道之中。他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于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16]
程颢这一段话十分重要,朱熹将其引入到他的代表著作《论语集注》的《雍也》篇中,可见这是理学家关于新仁学的思想共识。在这里,程颢采用了“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对“仁”作为天地万物之“体”和社会道德之“用”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别。一方面,程颢以《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论仁,他提出所谓“手足痿痹为不仁”“手足不仁,气已不贯”,就是从“生”的意义上论述对形而上之体的本体体认。他在多处既讲到人又讲到大自然的“生意”时,均视之以“仁”,如“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痒,谓之不仁”[17]。“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8],“观鸡雏,此可观仁。”19]这里的所谓“仁”,均是对作为“生”的“仁之体”的体认而言。另一方面,程颢谈到《论语》中的社会功利、道德方法方面的仁时,则强调这是仁之用,如孔子高度赞赏的“博施济众”的外在功业,以及他终身行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从“用”意义上的“为仁之方也已”。总之,无论是社会功利还是道德方法,如果从“体用之辨”的哲学角度来看,均是仁之体表现出来的不同“功用”而已。
程颐的仁学与程颢不一样[20],但是,以“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来建构新仁学,却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程颐的“体”是指“仁之理”,他同时主张:“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21]程颐希望通过天理来构建天地万物的终极依据,而这个天理恰恰来自于名教本身,是名教得以建立礼仪秩序的规范与准则。程颐的“理”就是指社会道德的规范,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程颐为《艮卦·彖传》作传时说:“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22]而且,此理在普天之下具有绝对的主宰性,即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3]程颐以“理”通天人、贯体用,完成了宋儒的天理论哲学建构。
三、南宋新仁学的完成
张载、二程是新仁学的奠基者,他们对仁学做出了两个重要发展,既实现《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的结合,又通过“体用”方法诠释仁学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二程建构的新仁学又引发出许多新的矛盾。他们希望天道与人道合一,又以体用之辩来诠释仁学,原本是要提升仁学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但是,程门弟子在新仁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对这一种新的仁学产生了许多歧义的理解,产生许多新的思想困扰和理论纷争。
其一,一些程门弟子沿着老师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仁的天道意义,反而忽略仁的人道意义。应该说,《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与“四书”“仁者爱人”“恻隐之心”的人道是有区别的。但是二程为了统合天道与人道,提升人道仁学的天道意义,反而突显天道“生物”的崇高价值,甚至以宇宙自然“生”的意义代替人与人之间“爱”的意义。如程门弟子谢上蔡往往直接以“生”以及与“生”有关的“知觉”“识”为仁,他认为天地自然的生生不息,特别是动物植物等有机体的生命现象就是“仁”。谢上蔡说:“仁者何也?活着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24]“有知觉、识痛痒,便唤作仁。”[25]这是将《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引入到人道而说仁,显然,这一种“仁”突显的是生物的自然天道意义,而不是人人相亲的人道意义。与此相关,他们认为“四书”中论述有关人道之仁的“爱人”“孝悌”“博施济众”,只是仁之用,不是他们所说的仁之体,谢上蔡说:“孝悌非仁也。”[26“博施济众,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于此得也。”[27]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天道意义的仁,才可以直接称之为“仁”;而一切人道意义的仁,反而不能够称之为仁。可见,谢上蔡为了提升“仁”的天道意义,反而贬低人道的仁。谢上蔡的看法并不是个别现象,这一看法影响了不少程门弟子。
其二,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是为了提高仁的本体意义,但是一些程门弟子因此而贬低了仁学的道德意义,否定了日用道德实践的修养工夫。由于二程以体用诠释“仁”,他们往往将仁看作是“天地之心”的形上本体,看作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天地境界,而对于“四书”原典所讲的人道之仁,诸如“忠恕”“爱人”“孝悌”“博施济众”等仁学的核心价值与修养工夫,均统言之以“用”。在“体用之辨”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中,“忠恕”“爱人”“孝悌”“博施济众”均归之于“功用”。与此同时,由于求仁工夫又可以分成追求天地境界的悟道工夫和道德境界的实践工夫。“四书”原典所讲的求仁工夫主要是道德日用工夫,但是,程门弟子往往表现出对追求天地境界的悟道工夫有更大兴趣。如谢上蔡直接以“知觉”“识”为仁,“知觉”“识”既是宇宙天地之“生”的本体,又是体悟宇宙天地之“生”的工夫,他理解的为仁之方是“知方所斯可以知仁,犹观天地变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心矣。”[28这显然是一种体悟天地之道、天地之心的“知”。另如杨龟山也倡导静中体悟的求仁工夫,他说:“君子之学,求仁而已。……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29]这一种求仁工夫,主要是追求超越天地境界的悟道工夫。事实上,许多儒家学者一味好高骛远,动辄讲“体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忽略了在日用伦常中的求仁工夫,甚至有些学者为显示自己的高明而贬低日用伦常的求仁工夫。
朱熹是洛学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接受、综合北宋各家理学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修正各种偏颇的思想言行。他希望这一正在蓬勃兴起的理学思潮,能够坚持儒家道德理性的发展理路。他的理学体系组成部分的仁学,就是北宋理学家群体新仁学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他希望新儒学能够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朱熹经过与湖湘学派张栻等人的交流、讨论,最终完成的《仁说》,为他进一步诠释“四书”的仁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仁说》一文中,可以看到朱熹为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朱熹首先以天人合一之道诠释仁学,努力完成天道与人道合一的仁学建构。朱熹《仁说》一文,将宋儒仁学从天道到人道、从人道到天道的两个过程做了论述,仁作为人道与天道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论述得十分系统,是宋儒建构天道与人道结合的新仁学体系的典范。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30]
朱熹《仁说》一文中,继承了北宋理学思想的传统,将《易传》的天道论仁学与“四书”的人道论仁学统一起来。朱熹一方面确立了仁作为“天地之心”的天道建构,作为天道的“仁”具有“元亨利贞”之四德、并且体现为“春夏秋冬之序”的自然秩序;另一方面,朱熹《仁说》又确立了仁作为“人心之妙者”的人道建构,作为人道的“仁”其实就是“仁义礼智”之四德,并且体现为“爱恭宜别之情”的人伦情感。可见,朱熹以“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为思想前提,将仁既是天道又是人道的特点做了清晰的论述。在朱熹看来,人心中之仁来源于“天地之心”,也就是如他所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为心者也。”[31]因此,人可以通过对人心之仁体认和实践,进而上达“天地之心”。可见,“天地以生物为心”体现出宇宙论意义的生生不息之天道,而“仁,人心也”的爱人之情,则是人“得夫天地之心为心”的人道。从生成论的角度,天道之仁产生了人道之仁;从道德论的角度,人道之仁的实践是遵循天道之仁的要求。
其次,朱熹又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仁可以实现天道和人道的相通。儒家的天道表达为“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的宇宙法则、自然秩序,它如何能够决定、主宰人道之仁呢?在理性主义的宋儒这里,“天道”不是一种神秘意志和人格力量,他们不相信神秘的天人感应。朱熹继承了二程以体用之辨诠释易学的思想传统,但是他特别强调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天道和人道能够相通的根本条件就在于“体”。朱熹在《仁说》一文接着说:
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以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32]
天道为什么能够体现出“天地生物之心”的仁道精神,源于其作为元亨利贞的“四德之体用”;同样,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的“人心之妙”,也是源于其仁义礼智的“四德之体用”。朱熹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特别强调应该从个体情感、社会伦常的“用”中,上达、完成形而上之“体”。因为仁之为体总是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这一个“仁之体”充盈宇宙天地、具体人物之中。任何个人均是“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以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那么,这一个作为统一天道和人道的形而上之“体”是什么?就是“理”,仁之理。为什么《易传》以“天之大德曰生”是天道之仁?朱熹解释是“只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它只知生而已。……缘他本原处有个仁爱温和之理如此,所以发之于用,自然慈祥恻隐。”[33]仁作为天道之理,总是通过万物生生不息来表达“仁爱温和之理”。同样,仁作为人道,也是仁之理在人伦日用、心理情感中的发用。朱熹在《仁说》一文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时说:“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34仁之理作为形而上之“体”,总是充盈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人生日用之中,它可以实现天道和人道的相通。
可见,朱熹通过天人合一、体用圆融之道诠释仁学,以推动新仁学的建构。与此同时,为了纠正程门弟子对新仁学的许多错误理解,他还在道学阵营内部,对一些道学家的仁学观点展开批判。朱熹在《仁说》一文中,在以天人合一、体用合一之道诠释仁学之后,又用了大量篇幅对程门弟子有关错误的仁学观展开了批判。
朱熹发现许多程门弟子并没有理解二程通过天人合一、体用合一之道诠释仁学的本意,为追求形而上之道及其天地境界,而忽略了儒学的人伦依据、情感基础,故而将天道与人道、体与用割裂、对立起来。譬如,根据体用合一之道的原则,性之体的仁和情之用的爱必须是紧密相连、彼此相通的。但是,一些程门弟子并没有理解程子“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的意思,将爱之情从仁道中分离出去,这就完全背离了儒家仁学的思想传统。所以,朱熹鲜明地批判“离爱而言仁”的错误思想,他说:“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35]朱熹坚决反对一些人将“仁”与“爱”二者“判然离绝”“判然离爱而言仁”的观点,因为这一种思想完全违背了儒家坚持的“体用合一”的思想传统。朱熹强调应该从“仁”的心理情感之用中体悟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体,仁既是体,又是用,是一种即用即体的道德情操和天理法则。
与此相关,朱熹进一步批判了程门后学中追求天道而忽略人道的思想倾向。一些理学学者好高骛远,对那一种与高远的天道相关的哲学思辨、形上境界特别偏好,他们或者仅仅以“生”以及与“生”有关的“知觉”“识”为仁,或者仅仅以“与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为仁。朱熹在《仁说》一文中批判了这一种为追求天道而忽略人道的思想倾向。他说:
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命之实也。……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知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知矣。[36]
原来,朱熹之所以要作《仁说》,是由于他担心程门弟子和道学家群体“泛言同体”“专言知觉”的现象,希望回归儒家正学。所以,朱熹强调:“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37]与此相关,仁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一种由人道而及天道的人文追求。那么,一切儒者必须坚持“四书”提出的求仁的下学工夫。可见,朱熹坚持体用圆融、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将早期儒学的仁学思想提升为一种体用一源、天人合一的思想学说,突显了儒家下学工夫的重要性。正如陈来先生所说,朱子“显然更注重仁说道德实践意义,即工夫意义,而不是仁说的境界意义。”[38]
在朱熹的《仁说》一文中,他将仁作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天道与人道的两个方面,做了很好的论述。为了充分表达天人合一、体用圆融之仁学,完成新仁学的建构,朱熹论仁时还提出“心之德而爱之理”的经典表述,他在《论语集注》的标准表述是:“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39]他强调从人道出发、下学而上达的仁学思想。他认为,仁的表现形式是爱的情感、心的知觉,体现了仁的人道特点;但是,他又强调仁的内容实质是“理”“德”“性”,仁作为“理”“德”“性”其实就是天道的人间形态。这样,朱熹的仁学既从天道到人道,又从人道到天道。朱熹在论述仁为什么离不开“情”“心”“性”时,继承了“四书”的人道学说和“克己”“存诚”等道德修身的下学工夫。朱熹在论述仁为什么是“理”“德”“性”时,继承了《易传》、汉儒的宇宙论仁学,借助于这一套宇宙论哲学,他建立起从天道到人道的仁学理论体系。宋儒建构的这种天道和人道合一的仁学,使得儒家的天道论与人道论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儒家的天道就不是一种冷漠的、死寂的、无意义的纯粹自然法则,而是具有美好情感、善意目的、正面意义的理性法则。另一方面,这一种具有美好情感、善意目的、正面意义的理性法则又不是一种神秘意志和人格力量,不是人可以通过宗教仪式、神秘巫术、献媚祈求而实现的。宋儒建构了一种既有理性精神又有人文情感的天道哲学。
儒家的人道论希望解决的是“仁义礼智”“爱恭宜别”的人文法则、个人情感问题,但是,由于这一人道不仅仅是“恻隐之心”,而且能够体现“天地之心”的宇宙精神。这样,儒家的仁道就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秩序、个体情感、求善目的的纯粹道德法则,而是具有形而上的、超越的、崇高精神的宇宙法则。以仁为中心的道德准则不会是一种功利的算计,也不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既扎根于人的心理情感的个体需求、宗法道德的社会需求,但是又能够充分表达一种超越个体心理情感、超越社会宗法道德,充分表达出仁道所具有的形上意义、崇高目的、宇宙精神。
宋儒建构和完成的新仁学,不仅是一种哲学化建构,同时也是一种价值信仰的重建。这一种新仁学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人格精神的仁获得了普遍的、永恒的宇宙意义,与此同时,冷漠的宇宙也开始充满仁的温情。
(原载《求索》2017年第8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宋儒通过重建“四书”的经典体系和重新诠释仁学,建构出一种天人合一、体用圆融的新仁学。这既是一种体用合一的哲学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信仰重建。宋儒如何完成儒家仁学的诠释与建构?宋明儒家新仁学的建构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何意义?
一、仁学的主体精神与形上依据
为了维护三代先王创造的礼乐文明,孔子创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从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意志的基本精神性要素,确立“仁”的基本内涵。经过孔子的仁学思想,作为三代文明核心的“礼”就不再是事神致福的手段,而是人心之“仁”的外在表达,体现出人的情感、理性、意志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说,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在人性以及人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意志的精神要素中,找到了“六经”之礼的人本依据。
孔子信奉、实践主体性精神的仁,必然面临主体精神的外在依据问题。孔子倡导为仁之道首先依赖于君子的自觉追求,但是仁道的外在实现还可能依赖于天命。他曾发出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孔子曾多次讲到“天”“天命”的主宰性力量,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畏天命。”[3]“天”是绝对不能获罪的,君子在“天命”面前必须保持敬畏、虔诚的态度,就是因为“天”“天命”对主体精神有强力的约束。所以,孔子不仅主张“畏天命”,同时也倡导“知天命”,他相信这一种具有主宰力量的“天”“天命”,应该是理性化的认知对象。可见,孔子的“仁”虽然能够确立“礼”的内在依据,但是,作为人的主体性精神的“仁”,如果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为准则和客观性社会现实,就必须表达出形而上的主宰力量。一切具有为仁的情感、理性、意志的人,必须要寻找、信仰一个外在的超越依据和最高主宰。
孔子后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人格精神与宇宙天道之间的联系,早期儒学的许多重要典籍如《子思子》《孟子》《易传》,也在思考和探讨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那些受到宋代儒家重视的早期儒家典籍,其实均是在探索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儒家诸子学的著作,儒家诸子试图为孔子的主体精神的仁心确立天道依据。
早期儒家探索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两种。
其一,从人道到天道,即从人的内在仁心领悟、提升出一种普遍性、崇高性的天道。《子思子》《孟子》论述了仁道的人性依据和最高主宰“天”的关系。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4]
在孟子那里,“天”“天命”主要是作为仁心、仁性的外在依据。那么,究竟什么是“天”“天命”呢?从《中庸》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天”“天命”是从主体性精神中提升起来的一种普遍性、崇高性的超越存在。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5]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6]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
这些论述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早期儒学努力探索仁之心性(人道)与天道之间的联系与特点。儒家思孟学派所讲的“天”“天道”既不是一种自然宇宙论,也不是一种宗教创世论,而是与人的情感、理性、意志的道德精神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存在,是一种希望通过主体性道德追求而提升出来的精神崇高性、价值普遍性。在《中庸》的思想中,“天道”无非是通过修炼而达到的“诚”的崇高人格,是一种“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精神境界。思孟学派肯定仁心、仁性是人的普遍性、崇高性特质,故而“天命之谓性”主要是强化仁心的精神崇高性、价值普遍性,以确立一种人文精神的信仰力量。
其二,从天道到人道,即从外在的自然天道论推导出仁义道德。《易传》是早期儒家探寻自然天道的哲学著作,它十分关心对宇宙自然之道的思考。《易传》在论述宇宙天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人道的要求。《易传·系辞》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易传·系辞》所描绘的宇宙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故而他们将“生”作为“天地之大德”。能够与“天地之大德”“生”相配的是圣人之“仁”,显然,他们认为人的“仁”之德与天的“生”之德具有相通的共性。由于《易传》旨在建构一个自然宇宙论,“生”才是“天地之大德”,“仁”不过是对“生”的仿效、追随。所以,《易传·系辞》总是将“仁”纳入到对“天地之大德”的仿效、追随:“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原来,“仁爱”只不过是伟大天道的显现与功用(“显诸仁,藏诸用”),是“与天地相似”“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具体表现。总之,《易传·系辞》是通过自然天道论来证明仁义的人道论。
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探索了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当然,他们的论证还存在一些不足。思孟学派是由人到天,《易传》是由天到人,但是这两种思想观念有什么关联,先秦儒家没有将两个不同理论体系打通,仁道论与天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他们的天道论、人道论显得太粗略,还不是精深的哲学化形上思辨。
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8]
董仲舒所论述的“仁”,完全是与人的心、志、气、欲等涉及人的情感欲望、精神意志等方面的因素有关,这正是对早期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他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关于仁之爱的观念,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强调:“故仁者所爱人类也。”[9]这一种“爱人类”的“博爱”思想,是传承孔子的仁学思想。
但是,另一方面,汉儒在关于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方面,则是继承三代时期天神上帝的宗教信仰。董仲舒比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仁与天神的关系,他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10]在董仲舒看来,人所具有的仁的情感与意志,其实是来源于“天”所具有的仁的情感与意志。而且,董仲舒吸收了西周时期“以德配天”思想,他所说的“天”完全是神灵之天。他认为“天”是具有仁的情感意志的“百神之大君”,人格神的“天”可以通过各种灾异向人类表达他的情感与意志,即所谓“谴告”。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宗教思想来建立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显然是继承了三代时期天神上帝信仰的体系,这与儒家的人文理性精神是不一致的。
二、北宋诸儒的新仁学
两宋儒家学者自觉承担“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在面临佛、道两教的严重挑战时,一方面回归儒家经典,努力恢复儒家仁学的人文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创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推动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宋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仁学,通过对仁学的创造性诠释,进一步确立仁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北宋是理学的奠基时代,北宋理学家也是新仁学的奠基人。宋儒建构新仁学固然与佛教的心性论、道家道教的宇宙论的挑战有关,但是新仁学的学术资源却是依据于先秦儒家经典。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典《易传》“四书”的创造性诠释,论证天道与人道结合的新仁学。“北宋五子”对新仁学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从《周易》的宇宙天道论仁学引申出“四书”的人道论仁学,实现了《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的结合。其二,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体用之辨”的诠释方法,对“四书”的人道仁学做出形上层面的本体论诠释,大大提升了仁学的哲学意义和精神信仰意义。
首先,我们探讨“北宋五子”新仁学的第一个贡献,考察他们如何从《周易》的自然主义天道论出发,引申出“四书”的人道主义仁学,建构出一种天道和人道一体化的新仁学。
本来,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两大类形而上学,一类是宇宙论的形而上学,一类是自我论的形而上学。而宋儒在重新建构新仁学时,则坚持将“宇宙论”与“自我论”两种形而上学统一起来,具体而言,就是将《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结合起来。他们既发挥《周易》的宇宙论思想资源,从而建构更具自然主义色彩的天道仁学;又通过诠释“四书”的心性仁学,从人的内在仁心提升出一个形而上的依据。而且,宋儒通过大量引入《易传》的思想资源,对“四书”仁学的创造性诠释,将思孟学派的心性仁学与《周易》的天道仁学结合起来,最终建构出一种天道和人道一体的新仁学。
周敦颐是理学奠基人,他的代表著作《太极图说》《通书》,均是将《周易》的宇宙论引申出仁义论的开创性著作。他的《太极图说》论述了太极的宇宙化生到圣人“立人极”的仁义道德的完成过程。周子《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原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原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11]这一个宇宙论哲学源于先秦、两汉的易学,但是,周敦颐的重要贡献是将《周易》的宇宙论与“四书”的仁义论结合起来,“四书”的仁义道德成为这个宇宙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仁义、主静是“立人极”的人道,它们与“无极而太极”的天道是相通的。周敦颐的经典依据主要是易学,他努力将《周易》的宇宙论与“四书”的仁义论结合起来,恰恰体现了从天道到人道的仁学思想特色。
张载从《易》学中引进了“气”的概念,他经过一番学术探索和思想整理,建立起“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他力图在“天人一气”的自然宇宙论基础之上,为儒家仁学思想做出宇宙本体论的论证。张载由天道自然到人道仁爱,大大拓展了儒家的哲学思想。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思想,这一仁爱思想的哲学基础却是“天人一气”的天道论。张载在论述仁者爱人的人道论时,处处表现出乾父坤母、天人一气的天道精神;同样,他在论述“乾坤”“天地之塞”“天地之帅”的天道原理时,其落脚点则是充满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张载在《西铭》中论述为仁之道的人道精神时,无处不在地透露出这一种人道意识与天人一气的天道意识的密切关联。他写道: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12]
张载在《西铭》中表达出一种对普遍性和永恒性仁爱精神的追求,尽管《西铭》中的仁爱精神是建立在宋代士大夫的主体精神与自我存在基础之上的,但是,“吾”之所以能够达到“仁之体”的心理状况和精神境界,完全源于天人一气的天道宇宙论。一个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仁爱精神的人,一定是能够具有、体认到天人一气的天道宇宙论的人。
二程也是从《周易》的宇宙论出发,将《周易》的天理论与“四书”的仁义思想结合起来,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理”成为一个存在于自然、社会中一切具体事物的普遍法则,更为重要的是,理不仅存在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之中,而且支配、主宰着世界的秩序和变化,故而,“理”又成为一个普遍、永恒的主宰者。从其主宰的绝对性而言,它又可以称之为“天”,他们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13]程颐还用“理一分殊”的新观点,来阐明“天理”在宇宙间的统一性问题。二程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乃至鬼神变化都依据于一个统一的天理。但是,天地之间的事物是各有重要区别的,君臣父子因尊卑长幼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事事物物各有其不同的道理。二程通过上述的学说论证,确立了一种以“天理”为中心的宇宙论,将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
其二,“北宋五子”新仁学还有第二个贡献,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体用之辨”的诠释方法,对“四书”的心性仁学做出本体论诠释,将“四书”的心性仁学上升到形而上之道,大大丰富了仁学的哲学意义。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有两种,一种是以汉儒为代表的天人同构、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一种是以宋儒为代表的体用之辨、同体异用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两宋时期,体用之辨成为宋儒诠释儒家经典的一个具有深刻哲学内涵和普遍意义的方法。宋儒通过诠释经典而为儒家的心性伦理建构起形而上的本体论思想体系,其建构本体论的基本方法就是体用论。宋儒通过一系列本体论的诠释后,仁学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仁学所表达的意思是十分世俗而实用的,但是经过宋儒的诠释,这些人伦日用的仁学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仁作为自然情感、交往理性、德性意志而有了形而上的升华,人道之体用就是天道之体用,人作为主体性的情感、理性、意志,最终可以与大本大源的天道、天理相通。
宋儒不满意汉儒以“天人感应”来建立仁心与天道之间的联系,他们重新回归到人的情感、理性、意志等精神要素,进一步确立“仁”的人道价值和意义。宋儒强调回归先秦儒学,因为从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之所以必须有仁爱的情感,并不是因为“人之受命于天也”,而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内在需求和心性呈现。所以,宋儒希望回归“四书”经典,从人的道德主体精神中追溯“仁”的源头。在宋儒许多经典论著和命题中,“仁”的依据总是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精神的“我”“己”“吾”。宋儒新仁学从人道到天道的哲学建构,首先是在吸收先秦思孟学派心性仁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宋儒在回归孔子以人的主体精神论仁的基础上,重新将仁归之于人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性、道德意志的精神心理要素。
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提升主体存在的形而上意义和价值,确立了主体之“仁”的天道意义和依据。宋儒在继承思孟学派心性仁学的基础上,努力从人的内在仁心提升出一个超越性的依据。他们特别关注《中庸》《孟子》,因为思孟学派的仁学是以心性论为基础的。宋儒通过对“四书”心性仁学的创造性诠释,最终使人道之“仁”与天道之“理”结合起来,完成了仁的形上哲学的建构。宋儒在确立仁的形上意义时,反复讲到“仁之体”,即是将作为主体道德精神的“仁”提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体”。程颢认为《西铭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14,意指张载在《西铭篇》中表达出的仁爱精神就是一种普遍和永恒意义的“体”。但是,我们会发现,程颢所讲的“仁之体”,并不是一种外在天地自然或宇宙世界的形而上之“体”,而首先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形而上之体,是以个体意识为基础的内在主体精神的“体”。
我们进一步来考察程颢对“仁之体”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程颢运用“体用之辨”的诠释方法对仁学做出本体论诠释。程颢在一篇专门讨论仁学的文章中说道: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比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在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15]
在这一段话中,程颢首先强调主体的“识仁”,“仁者”是一种“浑然与物同体”的心理状况和精神境界。可见,对宋儒来说,“仁体”首先是一种主体性存在,“识仁”也就是主体通过自己的直觉、体悟,获得对人、物的形而上之本体存在的直觉、境界。程颢的“识仁”,不是一种心之外的“防检”,更非心之外的“穷索”,而是对自己内在之心的察识,直接意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体悟到吾心之仁乃天地之仁,天地之仁亦吾心之仁。
由于宋儒对仁学采用了“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就更进一步融合了《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创建了一种本体论意义的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新仁学。程颢之所以相信仁者可以达到一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是因为这一种精神境界有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前提,即天和人背后有一个相通的形而上意义的“体”。程颢等理学家认为,这一个“体”就是《易传》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具有超越社会功利、道德价值的形上意义。程颢在建构新仁学时,肯定这一个具有“生”的本体贯串于天道和人道之中。他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于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16]
程颢这一段话十分重要,朱熹将其引入到他的代表著作《论语集注》的《雍也》篇中,可见这是理学家关于新仁学的思想共识。在这里,程颢采用了“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对“仁”作为天地万物之“体”和社会道德之“用”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别。一方面,程颢以《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论仁,他提出所谓“手足痿痹为不仁”“手足不仁,气已不贯”,就是从“生”的意义上论述对形而上之体的本体体认。他在多处既讲到人又讲到大自然的“生意”时,均视之以“仁”,如“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痒,谓之不仁”[17]。“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8],“观鸡雏,此可观仁。”19]这里的所谓“仁”,均是对作为“生”的“仁之体”的体认而言。另一方面,程颢谈到《论语》中的社会功利、道德方法方面的仁时,则强调这是仁之用,如孔子高度赞赏的“博施济众”的外在功业,以及他终身行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从“用”意义上的“为仁之方也已”。总之,无论是社会功利还是道德方法,如果从“体用之辨”的哲学角度来看,均是仁之体表现出来的不同“功用”而已。
程颐的仁学与程颢不一样[20],但是,以“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来建构新仁学,却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程颐的“体”是指“仁之理”,他同时主张:“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21]程颐希望通过天理来构建天地万物的终极依据,而这个天理恰恰来自于名教本身,是名教得以建立礼仪秩序的规范与准则。程颐的“理”就是指社会道德的规范,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程颐为《艮卦·彖传》作传时说:“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22]而且,此理在普天之下具有绝对的主宰性,即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3]程颐以“理”通天人、贯体用,完成了宋儒的天理论哲学建构。
三、南宋新仁学的完成
张载、二程是新仁学的奠基者,他们对仁学做出了两个重要发展,既实现《周易》的天道仁学与“四书”的人道仁学的结合,又通过“体用”方法诠释仁学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二程建构的新仁学又引发出许多新的矛盾。他们希望天道与人道合一,又以体用之辩来诠释仁学,原本是要提升仁学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但是,程门弟子在新仁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对这一种新的仁学产生了许多歧义的理解,产生许多新的思想困扰和理论纷争。
其一,一些程门弟子沿着老师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仁的天道意义,反而忽略仁的人道意义。应该说,《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与“四书”“仁者爱人”“恻隐之心”的人道是有区别的。但是二程为了统合天道与人道,提升人道仁学的天道意义,反而突显天道“生物”的崇高价值,甚至以宇宙自然“生”的意义代替人与人之间“爱”的意义。如程门弟子谢上蔡往往直接以“生”以及与“生”有关的“知觉”“识”为仁,他认为天地自然的生生不息,特别是动物植物等有机体的生命现象就是“仁”。谢上蔡说:“仁者何也?活着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24]“有知觉、识痛痒,便唤作仁。”[25]这是将《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引入到人道而说仁,显然,这一种“仁”突显的是生物的自然天道意义,而不是人人相亲的人道意义。与此相关,他们认为“四书”中论述有关人道之仁的“爱人”“孝悌”“博施济众”,只是仁之用,不是他们所说的仁之体,谢上蔡说:“孝悌非仁也。”[26“博施济众,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于此得也。”[27]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天道意义的仁,才可以直接称之为“仁”;而一切人道意义的仁,反而不能够称之为仁。可见,谢上蔡为了提升“仁”的天道意义,反而贬低人道的仁。谢上蔡的看法并不是个别现象,这一看法影响了不少程门弟子。
其二,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是为了提高仁的本体意义,但是一些程门弟子因此而贬低了仁学的道德意义,否定了日用道德实践的修养工夫。由于二程以体用诠释“仁”,他们往往将仁看作是“天地之心”的形上本体,看作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天地境界,而对于“四书”原典所讲的人道之仁,诸如“忠恕”“爱人”“孝悌”“博施济众”等仁学的核心价值与修养工夫,均统言之以“用”。在“体用之辨”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中,“忠恕”“爱人”“孝悌”“博施济众”均归之于“功用”。与此同时,由于求仁工夫又可以分成追求天地境界的悟道工夫和道德境界的实践工夫。“四书”原典所讲的求仁工夫主要是道德日用工夫,但是,程门弟子往往表现出对追求天地境界的悟道工夫有更大兴趣。如谢上蔡直接以“知觉”“识”为仁,“知觉”“识”既是宇宙天地之“生”的本体,又是体悟宇宙天地之“生”的工夫,他理解的为仁之方是“知方所斯可以知仁,犹观天地变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心矣。”[28这显然是一种体悟天地之道、天地之心的“知”。另如杨龟山也倡导静中体悟的求仁工夫,他说:“君子之学,求仁而已。……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29]这一种求仁工夫,主要是追求超越天地境界的悟道工夫。事实上,许多儒家学者一味好高骛远,动辄讲“体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忽略了在日用伦常中的求仁工夫,甚至有些学者为显示自己的高明而贬低日用伦常的求仁工夫。
朱熹是洛学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接受、综合北宋各家理学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修正各种偏颇的思想言行。他希望这一正在蓬勃兴起的理学思潮,能够坚持儒家道德理性的发展理路。他的理学体系组成部分的仁学,就是北宋理学家群体新仁学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他希望新儒学能够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朱熹经过与湖湘学派张栻等人的交流、讨论,最终完成的《仁说》,为他进一步诠释“四书”的仁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仁说》一文中,可以看到朱熹为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朱熹首先以天人合一之道诠释仁学,努力完成天道与人道合一的仁学建构。朱熹《仁说》一文,将宋儒仁学从天道到人道、从人道到天道的两个过程做了论述,仁作为人道与天道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论述得十分系统,是宋儒建构天道与人道结合的新仁学体系的典范。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30]
朱熹《仁说》一文中,继承了北宋理学思想的传统,将《易传》的天道论仁学与“四书”的人道论仁学统一起来。朱熹一方面确立了仁作为“天地之心”的天道建构,作为天道的“仁”具有“元亨利贞”之四德、并且体现为“春夏秋冬之序”的自然秩序;另一方面,朱熹《仁说》又确立了仁作为“人心之妙者”的人道建构,作为人道的“仁”其实就是“仁义礼智”之四德,并且体现为“爱恭宜别之情”的人伦情感。可见,朱熹以“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为思想前提,将仁既是天道又是人道的特点做了清晰的论述。在朱熹看来,人心中之仁来源于“天地之心”,也就是如他所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为心者也。”[31]因此,人可以通过对人心之仁体认和实践,进而上达“天地之心”。可见,“天地以生物为心”体现出宇宙论意义的生生不息之天道,而“仁,人心也”的爱人之情,则是人“得夫天地之心为心”的人道。从生成论的角度,天道之仁产生了人道之仁;从道德论的角度,人道之仁的实践是遵循天道之仁的要求。
其次,朱熹又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仁可以实现天道和人道的相通。儒家的天道表达为“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的宇宙法则、自然秩序,它如何能够决定、主宰人道之仁呢?在理性主义的宋儒这里,“天道”不是一种神秘意志和人格力量,他们不相信神秘的天人感应。朱熹继承了二程以体用之辨诠释易学的思想传统,但是他特别强调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天道和人道能够相通的根本条件就在于“体”。朱熹在《仁说》一文接着说:
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以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32]
天道为什么能够体现出“天地生物之心”的仁道精神,源于其作为元亨利贞的“四德之体用”;同样,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的“人心之妙”,也是源于其仁义礼智的“四德之体用”。朱熹以体用之辨诠释仁学,特别强调应该从个体情感、社会伦常的“用”中,上达、完成形而上之“体”。因为仁之为体总是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这一个“仁之体”充盈宇宙天地、具体人物之中。任何个人均是“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以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那么,这一个作为统一天道和人道的形而上之“体”是什么?就是“理”,仁之理。为什么《易传》以“天之大德曰生”是天道之仁?朱熹解释是“只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它只知生而已。……缘他本原处有个仁爱温和之理如此,所以发之于用,自然慈祥恻隐。”[33]仁作为天道之理,总是通过万物生生不息来表达“仁爱温和之理”。同样,仁作为人道,也是仁之理在人伦日用、心理情感中的发用。朱熹在《仁说》一文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时说:“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34仁之理作为形而上之“体”,总是充盈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人生日用之中,它可以实现天道和人道的相通。
可见,朱熹通过天人合一、体用圆融之道诠释仁学,以推动新仁学的建构。与此同时,为了纠正程门弟子对新仁学的许多错误理解,他还在道学阵营内部,对一些道学家的仁学观点展开批判。朱熹在《仁说》一文中,在以天人合一、体用合一之道诠释仁学之后,又用了大量篇幅对程门弟子有关错误的仁学观展开了批判。
朱熹发现许多程门弟子并没有理解二程通过天人合一、体用合一之道诠释仁学的本意,为追求形而上之道及其天地境界,而忽略了儒学的人伦依据、情感基础,故而将天道与人道、体与用割裂、对立起来。譬如,根据体用合一之道的原则,性之体的仁和情之用的爱必须是紧密相连、彼此相通的。但是,一些程门弟子并没有理解程子“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的意思,将爱之情从仁道中分离出去,这就完全背离了儒家仁学的思想传统。所以,朱熹鲜明地批判“离爱而言仁”的错误思想,他说:“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35]朱熹坚决反对一些人将“仁”与“爱”二者“判然离绝”“判然离爱而言仁”的观点,因为这一种思想完全违背了儒家坚持的“体用合一”的思想传统。朱熹强调应该从“仁”的心理情感之用中体悟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体,仁既是体,又是用,是一种即用即体的道德情操和天理法则。
与此相关,朱熹进一步批判了程门后学中追求天道而忽略人道的思想倾向。一些理学学者好高骛远,对那一种与高远的天道相关的哲学思辨、形上境界特别偏好,他们或者仅仅以“生”以及与“生”有关的“知觉”“识”为仁,或者仅仅以“与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为仁。朱熹在《仁说》一文中批判了这一种为追求天道而忽略人道的思想倾向。他说:
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命之实也。……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知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知矣。[36]
原来,朱熹之所以要作《仁说》,是由于他担心程门弟子和道学家群体“泛言同体”“专言知觉”的现象,希望回归儒家正学。所以,朱熹强调:“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37]与此相关,仁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一种由人道而及天道的人文追求。那么,一切儒者必须坚持“四书”提出的求仁的下学工夫。可见,朱熹坚持体用圆融、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将早期儒学的仁学思想提升为一种体用一源、天人合一的思想学说,突显了儒家下学工夫的重要性。正如陈来先生所说,朱子“显然更注重仁说道德实践意义,即工夫意义,而不是仁说的境界意义。”[38]
在朱熹的《仁说》一文中,他将仁作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天道与人道的两个方面,做了很好的论述。为了充分表达天人合一、体用圆融之仁学,完成新仁学的建构,朱熹论仁时还提出“心之德而爱之理”的经典表述,他在《论语集注》的标准表述是:“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39]他强调从人道出发、下学而上达的仁学思想。他认为,仁的表现形式是爱的情感、心的知觉,体现了仁的人道特点;但是,他又强调仁的内容实质是“理”“德”“性”,仁作为“理”“德”“性”其实就是天道的人间形态。这样,朱熹的仁学既从天道到人道,又从人道到天道。朱熹在论述仁为什么离不开“情”“心”“性”时,继承了“四书”的人道学说和“克己”“存诚”等道德修身的下学工夫。朱熹在论述仁为什么是“理”“德”“性”时,继承了《易传》、汉儒的宇宙论仁学,借助于这一套宇宙论哲学,他建立起从天道到人道的仁学理论体系。宋儒建构的这种天道和人道合一的仁学,使得儒家的天道论与人道论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儒家的天道就不是一种冷漠的、死寂的、无意义的纯粹自然法则,而是具有美好情感、善意目的、正面意义的理性法则。另一方面,这一种具有美好情感、善意目的、正面意义的理性法则又不是一种神秘意志和人格力量,不是人可以通过宗教仪式、神秘巫术、献媚祈求而实现的。宋儒建构了一种既有理性精神又有人文情感的天道哲学。
儒家的人道论希望解决的是“仁义礼智”“爱恭宜别”的人文法则、个人情感问题,但是,由于这一人道不仅仅是“恻隐之心”,而且能够体现“天地之心”的宇宙精神。这样,儒家的仁道就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秩序、个体情感、求善目的的纯粹道德法则,而是具有形而上的、超越的、崇高精神的宇宙法则。以仁为中心的道德准则不会是一种功利的算计,也不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既扎根于人的心理情感的个体需求、宗法道德的社会需求,但是又能够充分表达一种超越个体心理情感、超越社会宗法道德,充分表达出仁道所具有的形上意义、崇高目的、宇宙精神。
宋儒建构和完成的新仁学,不仅是一种哲学化建构,同时也是一种价值信仰的重建。这一种新仁学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人格精神的仁获得了普遍的、永恒的宇宙意义,与此同时,冷漠的宇宙也开始充满仁的温情。
(原载《求索》2017年第8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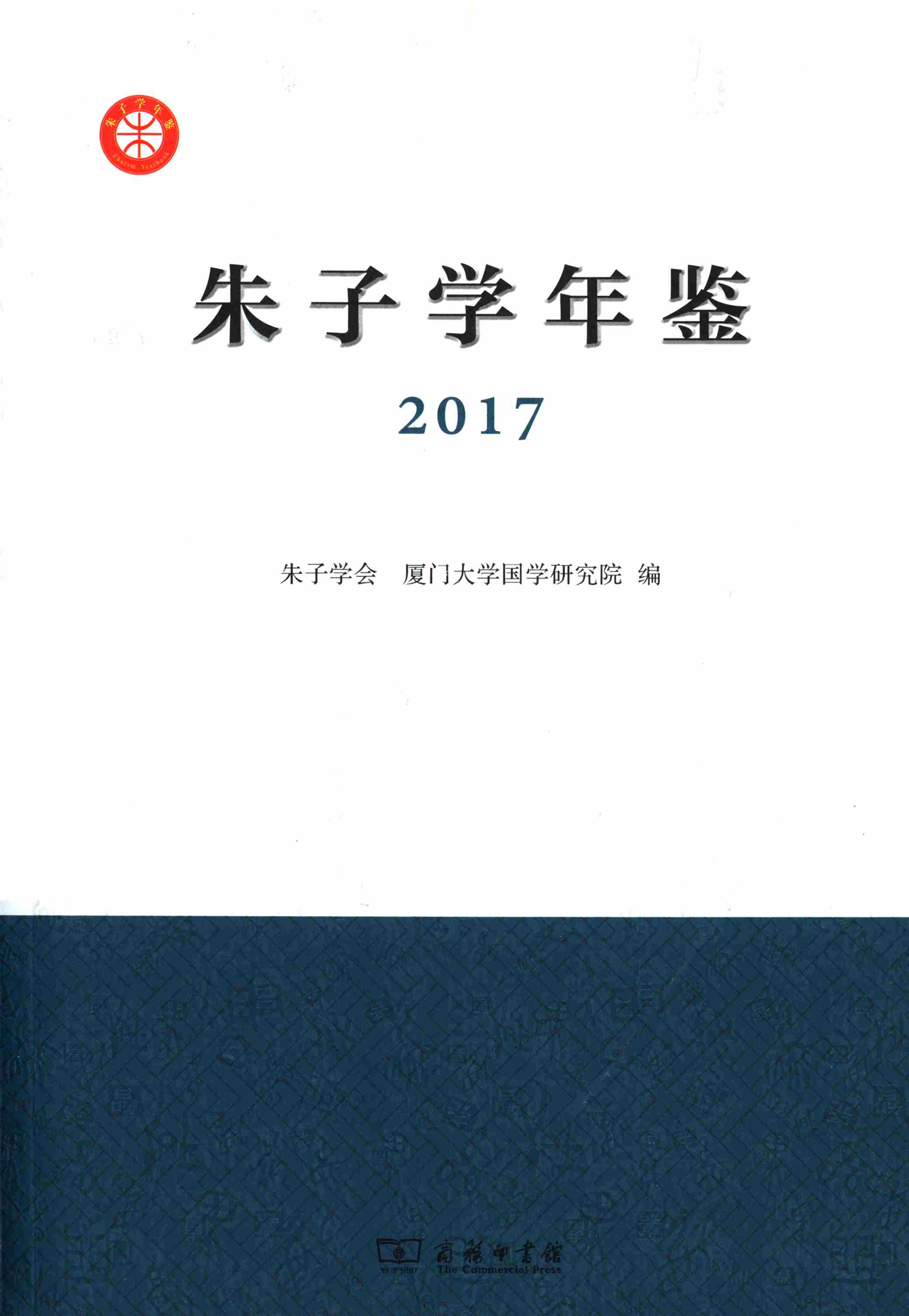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7》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仁者人也”新解》《朱子学的构建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朱熹与陈亮往来书信编年考证》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朱汉民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