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李朝朱子学的比较及特质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7》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106 |
| 颗粒名称: | 中国与朝鲜李朝朱子学的比较及特质 |
| 其他题名: | ——朱熹、退溪、栗谷、艮斋为例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3 |
| 页码: | 022-044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艮斋田愚对朝鲜复兴和民族文化保护的渴望和努力。他以苍龙和老树的比喻来表达对国家困境和侵略的忧虑,并希望民族能够重振雄风。他关注国家存亡,并致力于提升民族文化,抵制日本文化侵略。艮斋被誉为朝鲜末期性理学的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深厚,对深奥的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
| 关键词: | 民族大义 文化保护 学术造诣 |
内容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艮斋田愚(1841~1922)壮志不衰,不甘亡国,他胸怀满腔悲情,迫切期待朝鲜复兴;他以苍龙老树之身,挺民族脊梁,坚抗日意志,希冀“扶缐阳于既坠”,迎来民族之花的绽放。艮斋在民族存亡之际,忧国忧民,高扬民族大义,坚守民族文化,抗拒日本文化侵略。柳永善评说:“箕条邈焉,武夷道东。潭华继作,穷源会通。允集厥成,谁得正宗,曰我先生……文在于斯,天责归矣。心性理气,能所帅役。阐发蕴奥,朱栗准的。不得弗措,深思穷赜。小大无遗,允蹈其实。”[1]此说中其肯綮。艮斋学术造诣精湛,他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为朝鲜末之性理学大家。
一、朱熹、退溪、栗谷、艮斋理气观的异同
艮斋穷源会通箕子、朱子以来道统的正宗,沈潜经传,折衷百家,以朱熹(1130~1200)、栗谷(1536~1584)思想为标准,衡量性理学诸家。他在《晦退栗三先生说质疑》和《朱栗吻合》两文中提出了作为诠释者的立场、观点以及三先生理论思维逻辑的异同。退溪(1501~1570)、栗谷同为李朝朱子学大家,均以绍承、弘扬朱子学为职志,由于诠释的要旨、体贴的节点、思维的方式之间的差异而分殊。艮斋纠结于两人之间,而认同栗谷为朱子学的正脉,但不能以退溪为偏,诠释者在援本土文化融合朱子学时,就需要转换朱子学为本土朱子学,即朱子学的朝鲜李朝化,在这个转换中出现不同的体认,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所谓正脉与非正脉的分殊。因为退、栗的学术理论思维的宗旨,都是为了发展朝鲜朝朱子学,而纠佛教的空虚、空谈之弊,为化解“士祸”的政治、思想危机,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从理气关系而观,朱熹以理为形而上之道,以气、阴阳为形而下之器。作为形而上者,“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2]。这里反映出诸多疑难:究竟理在气先、气外,抑或在气后、气内?理能否动静?理不动,气为什么会动?“或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曰:不可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3]]朱熹觉得很难简单推究,故说:“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意度是一种意识、观念的推断,而非实存物理上的时空先后次序,若说理气先后,只能是一种逻辑上的气依傍理行的理先。“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这种先后之分,只是为确立理形而上存有的地位。确立理形而上先在地位,并不削弱气的地位,“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4]。“三无”是理本质内涵、特征和品格,作为气所依傍、所根据的理是一个纯粹的净洁的空阔世界。
朱熹既以“三无”规定理,便使理在动静上陷入尴尬,理若能动,便与其对理“三无”规定发生冲突,若理不动,依傍理的气如何动起来?理又如何到了气中?是什么能使其凝聚造作?朱熹只得说:“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5]“问:‘动静是太极动静?是阴阳动静?’曰:‘是理动静’。”[6]为了缓解“理有动静”说与理“三无”规定产生的紧张,朱熹从两方面对“理有动静”做了限制:就未发已发言,“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若以未发时言之,未发却只是静。动静阴阳,皆只是形而下者”[7]。太极(理)未发固然是静,“若对已发言之,容或可谓之太极,然终是难说。此皆只说得个仿佛形容,当自体认”。朱熹认为已发“中含喜怒哀乐,喜乐属阳,怒哀属阴,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就体用言,“动不是太极,但动者太极之用耳;静不是太极,但静者太极之体耳”[8]。以体用分理的动静,体相当于未发,用相当于已发。
太极(理)的动静问题颇使朱熹斟酌:“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此则庶几近之。’”[9]以“本然之妙”与“所乘之机”替代太极(理)的体用动静之说。什么是“本然之妙”与“所乘之机”:“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就本体而言,太极(理)蕴含着动静的潜能和根据;就流行而言,太极(理)有动静。但不能说太极就是动静,否则本体与流行、形而上与形而下就混同了。
朱熹进一步解释“所乘之机”说:“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10]乘是乘载之义,理乘载在气上,犹人乘载在马上。在这里朱熹回避了理自身会不会动静的问题,而留下不周延之处,若理不自动,人怎么骑到马上去?于是明初的曹端提出:“又观《语类》,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11假如太极(理)不自会动静,那么理与人便是死理、死人,如是,理与人便丧失了作为“万物之原”和“万物之贵”的价值和意义。[12]
朱熹对太极(理)能否自会动静做了不同的回答,给朝鲜性理学家的诠释留下空间。退溪与栗谷依据其对朱子学的体认与建构其理论思维逻辑体系的需要,以及援朱子学与朝鲜朝传统文化相融合、使朱子学韩国化的要求,对理(太极)能否动静做出了不同的诠释。退溪发挥朱熹理自能动静说,他说:“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13]退溪把朱子的“本然之妙”与“所乘之机”以体用关系,将其圆融起来,并改为“本然之体”与“至妙之用”的关系。体用圆融,并非混同,而是“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圣人纯于理,故静以御动”[14。这符合朱熹“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的思维逻辑,气为动静,理为所以动静的形而上之体,气为其作用和表现。这样退溪把曹端所说的“死理”,转死为活。当郑之云(1509~1561)作《天命图说》,退溪作后叙以奖之,并将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15]。奇高峰(1527~1572)认为此说有差误,高峰答书说:“今若以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则是理与气判而为二物也。是七情不出于性,而四端不乘于气也。此语意之不能无病,而后学之不能无疑也。”[16四端七情由不同理气而发,导致四端不乘于气,七情不出于性,而有割裂理气为二之弊。高峰坚持理气浑沦说。这是对退溪“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17]的回应。经此论辩,退溪最后改定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并改《天命图说》中的四端七情分别置于理圈与气圈之中,而成理发气发的图式。他在晚年所作的《圣学十图·第六心统性情图·下图》中,打破四七分别置于理圈与气圈的界限,而置于两边,凸显理气互发的关系。[18]
退溪的理气互发说,不仅说明理有动静、气亦有动静,理气相资、不离不杂。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在互发相须中,圆融无碍。[19]奇高峰主理气浑沦兼发,栗谷则主张气发理乘。三人都继承朱子学,但体认有异。栗谷从朱熹所规定理的“三无”出发,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而非退溪和奇高峰的理气互发或兼发论。栗谷说:“夫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非一物者,何谓也?理气虽相离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谓也?虽曰理自理,气自气,而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是故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理虽一而既乘于气,则其分万殊。”[20理为形而上的本体,是气的主宰,气是理的顿放、依著处,因而理气为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退溪发挥朱熹“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说,尽管朱熹已从体用、未发已发方面做了解释,以调和其对理性质“三无”的规定,但栗谷却从朱熹对理“三无”规定出发,而有退栗的理气互发说、气发理乘说。艮斋面对这两位朱子学双璧,又做何选择?明艮斋理气观,必先知其对理的规定。
其一,理无为、无声臭、无形。艮斋说:“据愚所闻,理无声臭,无兆联者。”[21]“今欲明理,理本无形”。[22]又在《理无为》中说:“夫理之无为的然,而何以为气之主。凡气之有为,若无此理为之根极则何以有成乎!此理之所以为不宰之宰,而有不使之使也。”[23]理无形、无为、无征兆、无迹象、无声臭。这是对理内涵、性质的规定,与朱熹的“三无”及栗谷以理无形、无为的规定相类,但艮斋认为理作为气的根本、根据,气的有为,是理不宰之宰,不使之使的使然。换言之,理具有主宰、指使气的逻辑潜能,这种潜能和根据是理作气之主的职责。
其二,理与道、太极、性相类。在艮斋理论思维的逻辑结构中,这些概念范畴具有相同的性质与地位。他说:“理字是道与性与太极之谓也。”“太极是本然之理”。[24“道者当然之理,皆性之德”。[25]“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26]在朱熹的哲学思维逻辑结构中,这四个范畴的性质、地位、作用是相互包含、融通的。[27]艮斋继承朱熹的逻辑思维,成为其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中的最高的形而上本体范畴,并由此推导出其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知识论、价值论、工夫论,以及“四七论”。
其三,理是至善的道德价值。艮斋说:“理是至善而万无一分未尽者也。”[28]此万无一分未穷尽至极至善的理,即仁义礼智四德之理,“以仁义礼智之性属于太极之理,而使心之存主运用,必本于性,而不敢自用焉”[29]。“仁是吾人身上本然之理,一定而不可易也”。[30]这是就其心三月不违仁而言的,“盖仁是天地生生之理,人得之以为性者也。仁固是温然有爱之理者也”[31]。仁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是充然有实的理等。理作为伦理道德的价值,应是无私欲的,“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32]。去人欲,而能复天理,才能做到明明德而新民,无过不及。
其四,天人合一的理。艮斋说:“余窃意天人无二道,亦无两气”。他引朱熹话说:“天人本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33]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天地万物之所以一体,是因为宇宙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而为地。理成为沟通、圆融天与人之间的媒介,否则天人如何合一?艮斋说:“愚窃谓天地生于理气,而又却将理气以生人物。天能生物,而不生于物,实则天亦生于理也。”[34天地人物都生于理气,既然同生于理气,便是体用一源,所以能合一。而实则生于理,因为宇宙间一理而已,此理为形而上的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的根据。尽管讲“天地生于理气”,以为是理气二元论,其实表明是理体一元论。艮斋凸显理体在其哲学逻辑结构体系中最高范畴的地位和作用,就为其气发理乘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艮斋论理,致广大而尽精微。在艮斋的心目中,气有为、有形、能发动。他引《朱子语类》:“太极理也,动静气也”。[35]尽管气有形,能动静,但不离理的使然。艮斋在《气能运理》中说:“愚尝言,上帝能运用太极,非太极运用上帝,气化能运用天道,非天道运用气化。”[36]虽然气有形、有动静,但气不是某一具体的器物,而是能虚灵知觉至神的气,“学者欲不宗朱子,则已如不欲畔朱子,须是将虚灵知觉之心,属于至神之气”[37],“气之精英者为神”[38]。这精英、至神的气是一个概念,是太极之理所乘的动态的概念,是生成万物的质料,或指浩然之气[39],亦指人物所具的气质。若以艮斋之气是某一具体器物,便是一个已生成之物,气就限定了,就不能作为生物的质料。
基于艮斋对理与气性质、特质、内涵的体认和其理论思维逻辑体系的需要,而在“四七”之辨中同意“气发理乘”说。艮斋认为,“朱子曰:四端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是性之理所在也。此段分明是栗翁气发理乘之渊源也”40。追根溯源,以栗谷的气发理乘是据朱子的思想而来,艮斋继承朱子和栗谷学说,这是其理论思维的前提。
二、朱熹、退溪、栗谷、艮斋心性论的异同
理气心性是性理学的核心话题,核心话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是不能离开思想而存在的,精神是思想着的精神,思想着的思想是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朝鲜李朝大儒通过核心话题的反复论辩,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把朝鲜民族的理论思维推向高峰,涌现出一大批理论思想家,这是民族灵魂的所在。
由四七理气之辨,自然推至心性之辨。退溪、栗谷、艮斋的心性论都依据其民族现实实践,绍承朱熹,而有所差分。朱熹认为,二程所讲的“性即理也”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性是人之所以得于天的理。他在注《中庸》“天命之谓性”时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人物之生,各得所赋的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是所谓的性。在朱熹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为形而上下的关系,转换为性与气,是“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41]。性既有形而上性,便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与理相似“性无形象、声臭之可形容也”。性具有“寂然至无”的特性。从体用而言,性体是“寂然不动”的,情用是“感而遂通”的。
朱熹依据《古文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分道心与人心,“道心者,天理也”[42],“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是无杂,惟一是终始不变,乃能允执厥中”[43]。道心全是天理,是四端四德的仁义礼智的善心。“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44],“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45]。但朱熹认为,简单地讲“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46]。上智的也不能无人欲,因此“人欲也未便是不好”。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船与舵的关系,“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柁,则去住在我”[47]。道心、人心只是一心,并非心外复有一心,理在人心谓之性,性得于天而具于心,理在心中,犹性在心中。
道心与人心的舵与船的关系,是由心性关系推导出的。其一,太极与阴阳关系。“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48]太极(性)是一,分阴阳为二,太极不离阴阳,二而一。“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其二,虚实辩证关系。“性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既虚又实,既实又虚。“性本是无,却是实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体却虚”。心为一物、似有影象,为一物体,其体又虚,性虚,却是实理,体现其辩证思维。这里所说心其体却虚,是指心的体用的心体而言。其三,动与所以动的关系。“问心之动,性之动,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49]心处在运动中,心的所以动是性。“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性理不动,心发用。其四,心性体用关系。“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犹如心为包子,性是包子的馅。性是心的所有的理,“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性体心用。其五,善恶关系。“心有善恶,性无不善。若论气质之性,亦有不善”。[50]尽管性善,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天命之性是天理,所以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和合,所以有不善。本心是善的,但后来做了许多不善的事,所以心有善恶。
退溪继承朱子性即理的思想。他说:“性即理也。则彼所谓五行之性,即此元、亨、利、贞之谓也。岂可谓彼无而此有之乎?”[51]人物各有其性,而无物无性,退溪在解释周敦颐“各一其性”时说,孔子讲“成之者性”,“各正性命”,孟子讲山性、水性等,性具有普遍性,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概念。性内在于心中。“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52]五常之性具于心中。性具心中,是性先动抑或心先动。“心之动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动即心之所以然也”。[53]性心的动不可分先后,“心非性,无因而为动,故不可谓心先动也;性非心,不能以自动,故不可谓性先动也”。心性的动,既互为动因,又互为动的所以然。退溪心性互动、互因是其理气互发说在心性论的贯彻,亦是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完整性的体现。这是对朱子“动处是心,动底是性”的修改,也与栗谷异。
退溪认为“夫理与气合而有心之名”[54,这是从构成论视阈规定心,但理气的性质不能不影响心的潜质和动能。他又细分心的不同层面:“以其本然之善,谓之良心;本有之善,谓之本心;纯一无伪而已,谓之赤子心;纯一无伪而能通达万变,谓之大人心;生于形气,谓之人心;原于性命,谓之道心。”[55]此“六心”各置图的不同位置,虽属道德意识范围,但是心的虚灵知觉的基础。心是思的器官,具知觉能力。“耳听皆有天则,而主之者心也”56,“知者,心之神明”[57]。心的知觉能力,亦可谓之神明,呈现为思维活动能力。心具万理,“盖人心虚灵不测,万理本具”[58]。心若虚灵不测,能动静万变,神化妙用,不失其则,就不会出偏差,不会被事物所蔽,不会被私意所囿。心作为神明升降之舍或精神力量,就其本然而言,无所谓善恶。心具有天人合一的普适性。“理气之合则为心,故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己之心即千万人之心,初无内外彼此之有异”。[59]内之一人之心,外之天地之心,一己之心与千万人之心,无有分别,通同为一。心具有能动性、贯通性、可入性、普遍性。
朱熹以道心为天理,或性命之正,合乎义理。退溪、栗谷继承朱子说,退溪认为道心是义理之心,固原于性命,是存天理、灭人欲而获得的。“遏人欲事,当属人心一边;存天理事,当属道心一边可也”。[60道心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或理想境界。退溪重道心、人心之别,栗谷则注意两者的联系。他说:“人心、道心非二心也。人心、道心既非二心,则四端七情亦非二情也。”61两者为一心。进而说:“朱子既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亦有人心矣,岂可尽谓之人欲乎?以此观之,则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62七情是人心、道心善恶的通称。并非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善为道心、恶为人心。七情包含道心,若说只指人心,只说对了一半。肯定人心有善的层面。道心为义理之心,是至善的,圣人所具有人心,出于性命之正,为四德四端的心,为朱、退、栗所同。至于对道心的追根溯源及道心范围的规定,退溪的发展,而异于朱子。栗谷从道心、人心的联系方面,说明七情是道心、人心善恶的总名,与朱子、退溪有异,即朱、退重一而二,栗谷重二而一,即一分一合。使道心、人心之辨以达圆满。
栗谷重道心、人心的二而一,是基于对心性为一路的体认。“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太差乎?须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63]所谓一心而各有境界,是指心的寂然不动时为性的境界,感而遂通是情的境界,因所感而抽绎商量的境界。虽心性情意各有境界,但不能分二而为一。从此思维逻辑出发,认为“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决非二性,特就气质上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之性耳,性既一,则情岂二源乎?……若如退溪之说,则本然之性在东,气质之性在西,自东而出者谓之道心,自西而出者谓之人心,此岂理耶?”[64]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性,而不同意退溪分东西两性,而分出道心与人心。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这是其“气发理乘”逻辑思维的贯彻,而与退溪理气互发异趣。
艮斋在心性论上,绍承朱栗,批评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即理说,并以形象的话语阐明性心关系。其一,“性是理之真体”。之所以是真体,是因为“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65]。性是人禀于天理,所以人与尧舜一样无差异;其二,“性是至善之理,不容修。扬雄言修性,是揠苗也”[66]。因为“人性全善而无些子偏恶”[67]。“性理全善而无恶;其三,“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心犹阴阳,太极为阴阳之主,而反为阴阳之所运用”[68]。在艮斋的思维逻辑结构中,理与太极同位,性是太极之体即性是理的真体;其四,性为义理之性。“义理之性,性与义理只是一物,非有二体可分。气质之性,性与气质只是一物,非有二物可指也”[69]。性与义理为一物,性之本就具有仁义礼智的义理内涵。“仁义礼智,吾儒之所谓性,而异学之所谓障也”[70]。性是伦理道德价值;其五,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艮斋在《气质之性》中开列五条:“第一,理在气中曰本然之性,而亦曰气质之性。如阴阳太极,形色天性,成之者性”71];“第二,理为气囿曰气质之性”;“第三,气质之禀,亦曰气质之性”;“第四,形气之欲,亦曰气质之性”;“第五,单指躯命,亦曰气质之性”[72]。这五种情况,均为气质之性,这是对气质在不同情境下的概括和体认。从气质之性来源说,“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合理与气质而命之曰气质之性。按气质之性是形而下之器也,气之局也”[73]]。气质之性为形而下者,是栗谷“理通气局”的气局的表现。从本然、气质不离而言,“离了气质更无性”。本然之性离了气质之性就无着落和安顿,气质之性离了本然之性就无根据和指导。此五层面为艮斋对性的规定,由此而可明心性之关系。
艮斋言心,其一,心为气,非理。“心事阴阳之属,无非是气”[74接栗谷心为气说,心气之上是至善大全不偏的理,然心非理。“心合乎理,则心非是理,而理为心本明矣”。[75]他屡批陆王“心宗家”心即理说,并认为退溪讲心合理气。[76]为维护栗谷心为气说:“心必待操而后存,则心之非理明矣,此栗翁所谓圣贤只要人检束其气而后复其本性者,所以为儒门尊性之道也”[77]。气与心是必须待澄明和操存的,理、天理不须澄明与操存,所以心非理。这是对心的内涵、性质规定理论前提。其二,为天地立心。“人君当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君心正,则天心豫而庆祥集焉,君心不正,则天心不豫而灾害至焉,天人感应昭然可见也”。[78]所谓君心正与不正,艮斋说:“圣人之仁如天地生物之心,有教无类,仁民爱众……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于方寸之中,是以逼人欲而存天理也”。[79]通过遏人欲,存天理,使人心得以正。其三,心为身之主。“心固是一身之主,然其所以主乎一身者,以其静而涵浑然之天,动而循粲然之天,而有妙用耳”。[80]心的动静若能涵浑然和循粲然之天,便有妙用。心主之能运用是因为“心为主宰,以心之存主运用,必本于性也”[81]。心本于性,才有主宰的功能。其四,心本善。“心之本善,亦以其有觉而知性至善,有力而体性之善也,故谓之本善也”。[82]心之所以说为本善,是因为其有觉有力而能知和体性的善的缘故。若保持其本善之心,就要不断地奋力振作。其五,心统性情辨。“心统性请,统犹兼也……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愚窃谓:善恶者皆出于天,情皆出于心,故曰天是统善恶的而言曰心统性情者也。若必以将帅统率军兵之实迹拟之,则天何尝统率夫恶,而行其号令;恶何尝拥护夫天而从其指麾,心安有指麾夫理而行其节制,理安有退听于心而遵其金鼓也哉。”[83]艮斋认为应先确立其思维逻辑体系的宗旨,而来体认其语意,“《朱子语类》季通云:心统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统名。”统名与统兵的统,语意内涵异趣。统名是“心统性情,是兼包该贯之义……非以尊统卑之谓也。”[84不是将帅统兵的尊卑关系。“朱子论心性情之分曰:横渠云:‘包性情者也,此说最为稳当,据此则统只见统总之义,非以尊卑之辞也’”。这样心统性情是心兼包、统总性情。这就为其“性尊心卑”“性师心弟”,性体心用,心本性等话题奠定基础和理论前提,也构建了其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一致性。
艮斋提出了既形象又有创见的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等主张。艮斋对于性尊心卑与性师心弟均有专章论述。其一,性尊心卑。在《性尊心卑的据》中,他从孔子、子思、孟子到二程、朱熹、尤庵共9条证据,并加按语:“性尊心卑不其明乎!”“万古最尊是性”,“以尊性为入道之门”,“性居尊位,而心从而尊之,则为儒者之学也。心不尊性而自尊焉,则为异端之学矣”。[85]又引朱子铭:“尊德性,希圣学。心若自尊而不肯尊性者,决是异学规模”86。心不能自尊而不尊性,这便是异端之学。其二,性师心弟。“性师心弟四字,是仆所创然。‘六经’数十万言,无非发明此理,可一以贯之。中夜以思,不觉乐意自生,而有手舞足蹈之神矣”。[87]“六经”之言,就是发明性师心弟的道理。“愚于性师心弟,虽未之能焉,而其自信之笃,亦可谓云尔已矣。古有心师、经师语,亦以心之师性,经之载道而言也”。[88]自古以来,心师性,他笃信性师心弟的创见是正确无误的。其三,就心本性言,艮斋著《心本性说》,认为“昔尝与朋友讲论得心本性三字,今以之做骨子”[89]。他用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道德关系来证明,心以性为根本、本体。“愚所谓心本性一句……学者苟能以此意善观圣贤经传,则句句是心本性,篇篇是心本性”[90]。此三层面,构成艮斋既接着朱子、栗谷心性论讲,与退溪有异,而又有自己独创性的诠释,其譬喻的通俗性,更易为民众所接受。
三、朱熹、退溪、栗谷、艮斋工夫论的会通
工夫论是为升华理想人格和风范,实现道德情操崇高境界,主体通过修身养性、居敬持志、主一无适、克去私欲的工夫,而完善其理气论、心性论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
朱子非常注重居敬穷理的道德修养工夫。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91]两者相资互发。居敬是持己之道,主体内在涵养工夫;穷理是格致之道,主体外在即物穷理工夫。从内在居敬而言,朱子认为“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92]。其妙处就在于“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93],心性存与不存,就在于敬。朱熹规定敬的工夫的内涵及功能:其一,敬乃圣门纲领。“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94]。敬极其重要,具有圣门的纲领和操存涵养的重要方法的地位,因此讲“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其二,敬具万理。“敬则万理具在”。“敬则德聚,不敬则都散了”。敬能凝聚道德天理,故“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主体人存得敬,吾心清澈澄明,天理显著美好。“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95]。即“存天理,灭人欲”之意。其三,敬为专一谨畏。“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96]把心收敛起来,不放逸而“始终一事”,“只敬,则心便一”。心一而谨畏,谨畏而专一,专一“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其四,敬为克己诚敬。“问持敬与克己工夫。曰:敬是涵养操持不走作;克己则和根打拼了,教他尽净”。[97]诚为诚实、诚信,去许多伪。其五,持敬的表现形式。“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严格’,‘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98]外在表现与内在思虑,内外表里如一。其具体表现“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99]。这是持敬的要求,并把其落实到行为的实践中,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缘由。
退、栗、艮结合其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朱熹的持敬涵养工夫。退溪说:“尝论持敬工夫。先生曰:‘如某者朝暮之顷,或有神清气定底时节,俨然肃然,心体不待把提而自存,四肢不待羁束而自恭,谨意以为古人气象,好时必是如此。’”100在朝暮很短的时间内,精神清朗,心绪安定,庄重整肃,心体不等有意而为便自存,四肢不等约束而自恭敬,这便是古人的持敬气象。退溪认为持敬与格物都不容易,若能认知持敬工夫方法,就能理明心定,格物就可明察,应事而不心累。
持敬涵养的内涵与价值:其一,以敬为本而有体用。“夫子尝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夫以敬为本,而有四者之事,岂不是兼该于体用”。[101]本有根本、本体之义,与四者之事的用对言,“静而严肃,敬之体也;动而齐整,敬之用也”102]。持敬的动静体用对举,体静为本,用动为本的表现或作用,是对程朱“以居敬穷理两言为万世立大训”[103]的发挥。其二,敬则心清气定。“盖怠惰则欲炽情流,而不宴不息,惟能敬则心清气定,而可以安养调息,故人能知宴息,亦以敬而非以怠惰,则可与论敬之理矣”。[104]只有敬使其内心清明,情绪安定,安静地修身养性。其三,主敬专一。“思明思聪等事,合在一时,思一不思二之疑,此则切问也……但所云一事方思,虽有他事不暇思之,此亦心无二用,主一工夫”。[105]主一工夫,就是心无二用。主事是无事有事湛然安静、随事应变。其四,正衣冠一思虑。李宏仲问:“若程夫子所谓敬者,亦不过曰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不欺不慢而已。”退溪说:“盖其曰正衣冠,曰庄整齐肃,是以静言。然而动时,衣冠岂可不整,容止事物岂可不庄整齐肃乎。曰一思虑,曰不欺不慢,是以动言。然而静时,此人尤不可不主于一,本原之地,又岂容有一毫欺慢乎”[106]。正衣冠,一思虑均是敬的内外体现,正衣冠,庄整齐肃,是敬表现一种视听言动方面的自律方式。一思虑,不欺不慢是敬的精神价值的体现。其五,持敬涵养。在《李子粹语》中特编“《涵养》一节,朱子指出;惟平日庄敬涵养,为本领工夫一节,尤为警切”。持敬是讲明心中之理,永保天理;涵养是培养心性本原,养心中之理。退溪说:“是以君子之学,当此心未发之时,必主于敬而加存养工夫。当此心已发之际,亦必主于敬而加省察工夫,此敬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而通贯体用者也”。[107]“省察”是指随时随事体察心中的理,“存养”是对于心性本原的培养,与涵养有相同之义。心未发时,主敬存养工夫,使本体心性达到完善。心已发时,主敬省察工夫,察识物理、纠其偏失,事事中节,反馈即物穷理以明心中之理。
退溪以敬为本、主一无适、心清气定、持敬涵养、正衣冠、一思虑的工夫论,其宗旨是明天理、去私欲。他比喻为磨镜工夫,镜本明,被尘垢所蔽而不明,心中理本明,被私欲所蔽,通过其工夫论,去尘垢(私欲),恢复其明。完善其理想人格,实现道德理想境界。
栗谷编纂《圣学辑要》五卷,他在《进札》中说明其价值:“凡帝王为学之本末,为治之先后,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皆粗著其梗概,推微识大,因此明彼,则天下之道实出此”[108],其宗旨是“圣贤之学,不过修己治人而已。今辑《中庸》《大学》首章之说,实相表里,而修己治人之道,无不该尽”[109]。《圣学辑要》就是围绕其宗旨而把修己、正家、为政之道结合起来,体现其人间性、实践性、生活性。就修己工夫而言,栗谷从立志、收敛、穷理、诚实、矫气质、养气、正心、检身、恢德量、辅德、敦笃、功效等十二个方面加以阐发,可见其致广大而尽精微。栗谷认为,修己工夫,必以“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明乎善,力行以践其实,三者终身事业也”[110]。本立而道生,故从居敬其本讲起:其一,居敬主一。“朱子曰:敬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间断。故此章大要义敬为主焉”[111]。要实现圣门第一义的敬,就要主一无适。“主一无适,敬之要法,酬酢万变,敬之活法……盖静中主一无适,敬之体也,动中酬酢万变,而不失其主宰者,敬之用也。非敬则不可以止于止善,而于敬之中又有至善焉。静非枯木死灰,动不纷纷扰扰,而动静如一;体用不离者,乃敬之至善也”。[112]朱子曾把主敬时的义,行义便有敬,敬义夹持,内外透彻,称为活法。栗谷称要法和活法,体用不离,动静如一,内外贯通,必须寡欲,“敬,主一之谓,从事于敬,则可以寡欲至于诚矣”[113],才能达到止善境界。其二,敬为圣学的始终。“敬者,圣学之始终也。故朱子曰:‘持敬是穷理之本,未知者,非敬无以知’。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言敬为学之始也。朱子曰:‘已知者,非敬无以守’。程子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此言敬为学之终也。今取敬之为学之始者,置于穷理之前”。114]圣学的始终都在于敬,持敬是穷理之本与入道之始,非敬无以守已知之理,立敬义,为圣学之终。其三,敬体义用。“敬体义用,虽分内外,其实敬该夫义,直内之敬,敬义存心也,方外之义,敬以应事也。”[115]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体用一原,直内方外,都是敬,只是存心与应事的差分。之所以都要敬,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方外是方方正正,自将去做圣门工夫。敬义夹持,直接上达天德。其四,恒主诚敬。“学者须是恒主于敬,顷刻不忘,遇事主一,各止于当止,无事静坐时,若有念头之发,则必即省觉所念何事,若是恶念,即勇猛断绝,不留毫末苗脉”。[116]时刻不忘主敬,不断克去恶念私欲,毫末不留,若是善念,穷理不断,使其明亮,回复本心之善。“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人不能复其本心者,由有私邪为之蔽也,以敬为主,尽去私邪,则本体乃全敬,是用功之要。诚是收功之地,由敬而至诚矣”。如何达到诚,由敬的去私欲、邪念的遮蔽,以回复本心的天理。其五,穷理涵养。“居敬为穷理之本”。117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穷理工夫大要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118]。此三项穷理工夫,均是主体向外通过即物、事、人、读书,而穷尽理,体认形而上的理本体。穷理工夫能否做到明义理、别是非、处当否,需要由极高明的主体内在卓越的素质、水准、判断智慧,这必须通过涵养工夫。“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119敬守此心,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此心寂静没有一毫思虑,在寂静中知觉清醒不昧,万象森然。只要涵养积久,就能穷理而理明。其六,敬贯知行。问“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此言何谓?曰:敬者通贯知行之间,故涵养致知,皆用敬焉”[120]。涵养致知知行内外、主体客体、知行兼备,通贯如一,以完善理想人格。“用功之至,必有效验,故次之以功效,以尽知行兼备,表里如一,入乎圣域之状”。[121]由敬知行,而通达道德价值理想的“圣域”境界,也是其修己工夫所达到的最崇高、最华彩的功效。
艮斋“某自谓主程、朱、栗”[122]。其实工夫论,也继承退溪。其一,敬为圣门工夫,“学者用功,将如何而可以矫治气质,而复还其性,只有敬以就中而已。天下道理只中一字便括尽圣门工夫,只敬一字便说尽”。[123]变化、矫治气质而恢复本然之性,“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敬就中,便可括尽圣门工夫,说尽穷理道理。“朱子曰:‘圣人只理会一个敬字。’……性以敬知性,以敬尽,只一敬而已。”[124]敬之价值与意义,艮斋及其重视。其二,敬功至精至微。“敬功至于无亏阙,无动摇,至精至微,至正至方,时时渊莹,处处圆融,方是尽处。若仅取一番操持,瞥然有主时便谓之敬,恐少间己,不可恃矣”[125]。敬的工夫,要做到无缺无动摇,精微方正,渊莹圆融,才是敬工夫的尽处,不是操持一番就可以的,要坚持不懈地去用功;其三,敬为北斗。“敬者,心之所以为主宰也。只言心则只是虚灵精妙之气耳。著个敬字工夫,如舟在大洋中不辨方向,而仰见北斗,始有子午可指。心而无敬便放倒,无复可以承夫理而宰乎身者也。”[126]心为气,心如大洋中的船,它不辨方向,敬如北斗,北斗指示方向,才能使大洋中船到达目的地,敬是心的主宰。“敬字工夫至则此心有事时,洞然外达。无事时,卓然中立。动而不累于物,静而不沦于空,此是敬功至妙处,然极难得力。”[127]“窃观圣人只一心敬,而万务皆叙。我辈学者只一舌敬,而百体皆肆,是所谓言行不相副也。”[128]圣人诚心为敬,万般事务都能澄明,若口头讲敬,放肆行为,便犯言行不副的病症;其四,敬则道凝。“敬则道凝而德成,不敬则道亏而德败,圣人聪明睿智,故自然能敬……今我辈学者,须勉强于敬功,时时处处必靠著敬字以为骨子。”[129]敬作为道德价值的凝聚与亏损,直接关系道德价值的成败,从这个意义说,敬是主心骨。其五,诚敬为万善骨子。“诚敬二字,吾儒以之为万善骨子……朱先生教门人云:学者之心,大凡当以诚敬为主。”[130]批评心宗学者如陆九渊等不以诚敬为主的偏颇。诚敬之所以是万善骨子,是因为“敬以明理,诚以从道,此两句工夫尽时,已是换凡骨以接圣脉。”[131]敬诚的价值在明理从道,此工夫做尽,就能脱凡骨换圣脉的转生。其六,敬贯知行。“学问之道有四,格致、存养、省察、力行,而存养贯始终,此晦翁敬贯知行之说也。”[132]“敬皆包得知行在内,不可一时一事不用诚敬也。余每谓有意时诚行焉,无意时诚立矣,格致时敬行焉,诚正时敬立矣。”人不可须臾离开诚敬,时时事事要用诚敬,格物致知是敬的行为,诚意正心是敬的确立。敬贯知行,需通过存养、省察工夫,如“庄敬整齐以自持于言动事为之间。”[133]“学者工夫,只有操心治气,以顺其性一事而已,”[134]以达存天理,去私欲的境界。艮斋工夫论以敬为核心话题,与退溪、栗谷会通,而有所发挥,以敬为北斗,为指针。
四、朱熹、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精神的特质
朝鲜朱子学的双璧退溪和栗谷生活在燕山君与宣祖时代,当时天灾频仍,经济凋敝,人祸迭起,生灵涂炭。执政者内部斗争激烈,往往与“士祸”相终始,使诸多性理学家遭受杀身之祸。艮斋生活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为日本侵略者占据的时期,他誓死与其不共戴天。退、栗、艮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济民的悲愿,以自己终生的忧患去担当忧道、忧国、忧民的大任,以自己民族大义的思想精神感召大众去实现“天理”的人间世。他们的思想精神特色是:
其一,义理精神。性理学家以求理为宗旨,以存天理为目标,以居敬、涵养、知行为工夫,在国家危机、民族灾难之际,为挺立民族脊梁而弘扬义理精神,为忧国忧民、经世济民而担当历史使命,成为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精神与实践活动的核心内涵,体现了其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退溪在《戊辰六条疏》中的第一条就是“重继统以全仁孝”。孝为百行之原,仁为万善之长,一行有亏与一善不备,就不能全仁孝。第三条为敦圣学以立治本。帝王和常人都应以“敬以为本,而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为原则。第四条明道义以正人心,都凸显了其义理精神。退溪和栗谷义理精神表现在对四次“士祸”的忧患上,认为有损国脉,有害社会正义。他们痛心疾首,忧患再次发生“士祸”。因而提倡圣人之学,退溪造《圣学十图》,栗谷编纂《圣学辑要》,从圣学的各个层面,为性理学的义理精神规划了理气观、心性论、工夫论的内涵、性质的方向和实践活动的路径。艮斋在辱权丧国的患难中,坚守民族义理精神和礼仪大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变服、断发令。他决不“牵制于仇虏之手……窃以为中正之道也”[135],后决意“入海守道,讲明大义,以扶缐阳于既坠”[136]。这是弘性理学义理精神,扬民族中正大义精神。
其二,敬诚精神。性理学家道德理想的实践,修身养性的实现,道德情操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完善,都需要通过敬诚的多方面不断培育,以达人生最高境界。退溪、栗谷、艮斋弘扬朱子理体学,“朱熹自少有志于圣道,为其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137]。从经旨不明,道统之传昏暗,朱子竭其精力研究穷尽圣贤的经典古训,他所著的书为学者所宗。退溪以敬为本而有体用,主一无适,持敬涵养,心清气定,反躬践其正衣冠,一思虑,以去私欲明天理。栗谷提倡敬是圣学的始终,主一主事于敬,便可以寡欲而至于诚。恒主诚敬,发扬善念,断绝恶念。居敬以穷理为本,由敬而至于诚,只要涵养积久,就能穷理而理明,存养知行,都需要敬,因为敬贯知行之间,而彰显躬身实践诚敬的功效,而达道德价值理想的“圣域”境界。艮斋以圣门工夫敬可说尽,敬是北斗、指南针,是航行于大洋中不迷失方向的子午。敬至精至微,渊莹圆融,圣人诚心为敬,万般事务澄明,诚敬是人的主心骨,它是万善的骨子,人须臾不离诚敬,从不间断,无所不贯,贯通知行。诚敬为立本的工夫,本立而达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理想境界。
其三,创新精神。退溪、栗谷、艮斋在义理、诚敬精神的大本大志、大是大非的地基上,建起了其新性理学的大厦,其间创新是新大厦之所以新之所在,是新之所新的生命和灵魂。创新是既继承又超越,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新瓶装新酒。在理气观上,退溪着眼于朱子理的“三无”说,而化解被曹端所质疑的困境,主张理自会运动说,“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生气也”[138]。因而“四端七情”之辨中主理气互发说,这是对理的动静的创新。栗谷的“理气妙合”和“理通气局”说,亦是对朱子理气观的发展和创新,他们既赋予理气观以新生命,也是朱子理气观转生为朝鲜朝理气观的实现,换言之,退溪、栗谷的理气观是转生朝鲜朝朱子学的关键节点。由理气观而推致心性论,退溪认为理气合有心之名,并将心细分为六层面,对道心、人心之辨的追根溯源和道心范围的规定是其发展。栗谷重道心、人心的二而一,圆融无碍。艮斋提出“心本性”“性尊心卑”。
“性师心弟”说是对朱熹、退溪、栗谷心性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论思维逻辑的创新是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精神价值所在,唯有创新才能生生不息,唯有发展才能完善朝鲜朱子学——朝鲜性理学,使之永垂不朽。
其四,逻辑精神。这里是指其理论思维体系的概念范畴的逻辑结构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或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哲学思想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哲学思想概念范畴按逻辑顺序或结合方式构成的,并从整体的逻辑结构上,确定诸概念范畴在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就是说哲学思想史作为观念逻辑的演变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概念范畴发展史。就本文所论之理、气、心、性、敬、诚等概念范畴而言,各哲学家其概念范畴在其哲学思想逻辑结构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正说明不同概念范畴在其哲学逻辑结构体系中的差分,如退溪主理,栗谷主气,艮斋讲性尊心卑、性师心弟,为其明证。又如退溪《圣学十图》、栗谷的《圣学辑要·目录图》、艮斋的《命性图》等,每图都将其最高的核心概念范畴置于图式的最高位置,对整图有统摄意义和价值。他们都曾以图式的形式来表现其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体系,每造一图都是他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精华所在。退溪的《圣学十图》是:“或抽绎玩味于夜气清明之时,或体验栽培于日用酬酢之际,其初犹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时有极辛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谓将大进之几,亦为好消息之端。”[139]可体会其为造《圣学十图》的殚精竭虑的心得,是从日夜辛苦中得来。栗谷的《圣学辑要》是“深探广搜,採掇精英,汇分次第,删繁就要,沈潜玩味,反复櫽括”[140],反复剪裁改写、取其精华而成的,其得来不易。艮斋的《命性图》是与“湖中士友相与虚怀讲究,而解此迷蒙,实平生切愿尔”[141]所完成的。这些图式化的概念范畴逻辑结构,是其概念范畴运动形式以及各概念范畴之间相对稳定的排列顺序或结合方式,它是各概念范畴逻辑结构内各个层次、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作用总和的表现方式和逻辑思维的形式。
其五,笃行精神。学问思辨,逻辑思维、理气心性、价值观念,都要落实到行上,无笃行,理论思维是空虚、是无生命力的,也不会持久和生生不息。退溪认为居敬要落实到实际行为之中,如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并落实到家道、家规上。“凡为子孙,当谨守家法。”142]如果任意忘礼,废三世家规,这是很严重的事故。栗谷所规划的修己正家为政之道,把正家落实到孝敬、刑内、教子、亲亲、谨严、节俭上;为政落实到用贤、取善、识务、法先王、谨天戒、立纪纲、安民、明教上143],都是讲日用之学。艮斋认为居敬、涵养、省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言行一致,在《家规》中规定得很仔细,从孝敬、守家礼到冠婚丧祭礼的实行,以及女子必令读女戒女范等无所不及。在《蓍洞书社仪》中规定“就座展卷,端庄肃敬,如对圣贤、从容诵读,仔细究索,不得与人说话,不得无事出入”144。在《凤寺山房规约》中规定“读书须整襟端坐,正置册子,专心诵念,勿高声,勿摇身,少顷掩卷思绎,务令指意分明,义理浃洽”[145]。退溪、栗谷、艮斋都是以身作则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实践家、思想家、哲学家。正是这种笃行精神,使其思想精神在现实中光彩夺目,为人所敬仰,为后世所高山仰止。
一、朱熹、退溪、栗谷、艮斋理气观的异同
艮斋穷源会通箕子、朱子以来道统的正宗,沈潜经传,折衷百家,以朱熹(1130~1200)、栗谷(1536~1584)思想为标准,衡量性理学诸家。他在《晦退栗三先生说质疑》和《朱栗吻合》两文中提出了作为诠释者的立场、观点以及三先生理论思维逻辑的异同。退溪(1501~1570)、栗谷同为李朝朱子学大家,均以绍承、弘扬朱子学为职志,由于诠释的要旨、体贴的节点、思维的方式之间的差异而分殊。艮斋纠结于两人之间,而认同栗谷为朱子学的正脉,但不能以退溪为偏,诠释者在援本土文化融合朱子学时,就需要转换朱子学为本土朱子学,即朱子学的朝鲜李朝化,在这个转换中出现不同的体认,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所谓正脉与非正脉的分殊。因为退、栗的学术理论思维的宗旨,都是为了发展朝鲜朝朱子学,而纠佛教的空虚、空谈之弊,为化解“士祸”的政治、思想危机,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从理气关系而观,朱熹以理为形而上之道,以气、阴阳为形而下之器。作为形而上者,“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2]。这里反映出诸多疑难:究竟理在气先、气外,抑或在气后、气内?理能否动静?理不动,气为什么会动?“或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曰:不可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3]]朱熹觉得很难简单推究,故说:“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意度是一种意识、观念的推断,而非实存物理上的时空先后次序,若说理气先后,只能是一种逻辑上的气依傍理行的理先。“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这种先后之分,只是为确立理形而上存有的地位。确立理形而上先在地位,并不削弱气的地位,“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4]。“三无”是理本质内涵、特征和品格,作为气所依傍、所根据的理是一个纯粹的净洁的空阔世界。
朱熹既以“三无”规定理,便使理在动静上陷入尴尬,理若能动,便与其对理“三无”规定发生冲突,若理不动,依傍理的气如何动起来?理又如何到了气中?是什么能使其凝聚造作?朱熹只得说:“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5]“问:‘动静是太极动静?是阴阳动静?’曰:‘是理动静’。”[6]为了缓解“理有动静”说与理“三无”规定产生的紧张,朱熹从两方面对“理有动静”做了限制:就未发已发言,“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若以未发时言之,未发却只是静。动静阴阳,皆只是形而下者”[7]。太极(理)未发固然是静,“若对已发言之,容或可谓之太极,然终是难说。此皆只说得个仿佛形容,当自体认”。朱熹认为已发“中含喜怒哀乐,喜乐属阳,怒哀属阴,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就体用言,“动不是太极,但动者太极之用耳;静不是太极,但静者太极之体耳”[8]。以体用分理的动静,体相当于未发,用相当于已发。
太极(理)的动静问题颇使朱熹斟酌:“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此则庶几近之。’”[9]以“本然之妙”与“所乘之机”替代太极(理)的体用动静之说。什么是“本然之妙”与“所乘之机”:“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就本体而言,太极(理)蕴含着动静的潜能和根据;就流行而言,太极(理)有动静。但不能说太极就是动静,否则本体与流行、形而上与形而下就混同了。
朱熹进一步解释“所乘之机”说:“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10]乘是乘载之义,理乘载在气上,犹人乘载在马上。在这里朱熹回避了理自身会不会动静的问题,而留下不周延之处,若理不自动,人怎么骑到马上去?于是明初的曹端提出:“又观《语类》,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11假如太极(理)不自会动静,那么理与人便是死理、死人,如是,理与人便丧失了作为“万物之原”和“万物之贵”的价值和意义。[12]
朱熹对太极(理)能否自会动静做了不同的回答,给朝鲜性理学家的诠释留下空间。退溪与栗谷依据其对朱子学的体认与建构其理论思维逻辑体系的需要,以及援朱子学与朝鲜朝传统文化相融合、使朱子学韩国化的要求,对理(太极)能否动静做出了不同的诠释。退溪发挥朱熹理自能动静说,他说:“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13]退溪把朱子的“本然之妙”与“所乘之机”以体用关系,将其圆融起来,并改为“本然之体”与“至妙之用”的关系。体用圆融,并非混同,而是“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圣人纯于理,故静以御动”[14。这符合朱熹“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的思维逻辑,气为动静,理为所以动静的形而上之体,气为其作用和表现。这样退溪把曹端所说的“死理”,转死为活。当郑之云(1509~1561)作《天命图说》,退溪作后叙以奖之,并将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15]。奇高峰(1527~1572)认为此说有差误,高峰答书说:“今若以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而有善恶,则是理与气判而为二物也。是七情不出于性,而四端不乘于气也。此语意之不能无病,而后学之不能无疑也。”[16四端七情由不同理气而发,导致四端不乘于气,七情不出于性,而有割裂理气为二之弊。高峰坚持理气浑沦说。这是对退溪“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17]的回应。经此论辩,退溪最后改定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并改《天命图说》中的四端七情分别置于理圈与气圈之中,而成理发气发的图式。他在晚年所作的《圣学十图·第六心统性情图·下图》中,打破四七分别置于理圈与气圈的界限,而置于两边,凸显理气互发的关系。[18]
退溪的理气互发说,不仅说明理有动静、气亦有动静,理气相资、不离不杂。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在互发相须中,圆融无碍。[19]奇高峰主理气浑沦兼发,栗谷则主张气发理乘。三人都继承朱子学,但体认有异。栗谷从朱熹所规定理的“三无”出发,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而非退溪和奇高峰的理气互发或兼发论。栗谷说:“夫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非一物者,何谓也?理气虽相离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谓也?虽曰理自理,气自气,而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是故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理虽一而既乘于气,则其分万殊。”[20理为形而上的本体,是气的主宰,气是理的顿放、依著处,因而理气为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退溪发挥朱熹“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说,尽管朱熹已从体用、未发已发方面做了解释,以调和其对理性质“三无”的规定,但栗谷却从朱熹对理“三无”规定出发,而有退栗的理气互发说、气发理乘说。艮斋面对这两位朱子学双璧,又做何选择?明艮斋理气观,必先知其对理的规定。
其一,理无为、无声臭、无形。艮斋说:“据愚所闻,理无声臭,无兆联者。”[21]“今欲明理,理本无形”。[22]又在《理无为》中说:“夫理之无为的然,而何以为气之主。凡气之有为,若无此理为之根极则何以有成乎!此理之所以为不宰之宰,而有不使之使也。”[23]理无形、无为、无征兆、无迹象、无声臭。这是对理内涵、性质的规定,与朱熹的“三无”及栗谷以理无形、无为的规定相类,但艮斋认为理作为气的根本、根据,气的有为,是理不宰之宰,不使之使的使然。换言之,理具有主宰、指使气的逻辑潜能,这种潜能和根据是理作气之主的职责。
其二,理与道、太极、性相类。在艮斋理论思维的逻辑结构中,这些概念范畴具有相同的性质与地位。他说:“理字是道与性与太极之谓也。”“太极是本然之理”。[24“道者当然之理,皆性之德”。[25]“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26]在朱熹的哲学思维逻辑结构中,这四个范畴的性质、地位、作用是相互包含、融通的。[27]艮斋继承朱熹的逻辑思维,成为其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中的最高的形而上本体范畴,并由此推导出其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知识论、价值论、工夫论,以及“四七论”。
其三,理是至善的道德价值。艮斋说:“理是至善而万无一分未尽者也。”[28]此万无一分未穷尽至极至善的理,即仁义礼智四德之理,“以仁义礼智之性属于太极之理,而使心之存主运用,必本于性,而不敢自用焉”[29]。“仁是吾人身上本然之理,一定而不可易也”。[30]这是就其心三月不违仁而言的,“盖仁是天地生生之理,人得之以为性者也。仁固是温然有爱之理者也”[31]。仁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是充然有实的理等。理作为伦理道德的价值,应是无私欲的,“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32]。去人欲,而能复天理,才能做到明明德而新民,无过不及。
其四,天人合一的理。艮斋说:“余窃意天人无二道,亦无两气”。他引朱熹话说:“天人本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33]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天地万物之所以一体,是因为宇宙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而为地。理成为沟通、圆融天与人之间的媒介,否则天人如何合一?艮斋说:“愚窃谓天地生于理气,而又却将理气以生人物。天能生物,而不生于物,实则天亦生于理也。”[34天地人物都生于理气,既然同生于理气,便是体用一源,所以能合一。而实则生于理,因为宇宙间一理而已,此理为形而上的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的根据。尽管讲“天地生于理气”,以为是理气二元论,其实表明是理体一元论。艮斋凸显理体在其哲学逻辑结构体系中最高范畴的地位和作用,就为其气发理乘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艮斋论理,致广大而尽精微。在艮斋的心目中,气有为、有形、能发动。他引《朱子语类》:“太极理也,动静气也”。[35]尽管气有形,能动静,但不离理的使然。艮斋在《气能运理》中说:“愚尝言,上帝能运用太极,非太极运用上帝,气化能运用天道,非天道运用气化。”[36]虽然气有形、有动静,但气不是某一具体的器物,而是能虚灵知觉至神的气,“学者欲不宗朱子,则已如不欲畔朱子,须是将虚灵知觉之心,属于至神之气”[37],“气之精英者为神”[38]。这精英、至神的气是一个概念,是太极之理所乘的动态的概念,是生成万物的质料,或指浩然之气[39],亦指人物所具的气质。若以艮斋之气是某一具体器物,便是一个已生成之物,气就限定了,就不能作为生物的质料。
基于艮斋对理与气性质、特质、内涵的体认和其理论思维逻辑体系的需要,而在“四七”之辨中同意“气发理乘”说。艮斋认为,“朱子曰:四端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是性之理所在也。此段分明是栗翁气发理乘之渊源也”40。追根溯源,以栗谷的气发理乘是据朱子的思想而来,艮斋继承朱子和栗谷学说,这是其理论思维的前提。
二、朱熹、退溪、栗谷、艮斋心性论的异同
理气心性是性理学的核心话题,核心话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是不能离开思想而存在的,精神是思想着的精神,思想着的思想是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朝鲜李朝大儒通过核心话题的反复论辩,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把朝鲜民族的理论思维推向高峰,涌现出一大批理论思想家,这是民族灵魂的所在。
由四七理气之辨,自然推至心性之辨。退溪、栗谷、艮斋的心性论都依据其民族现实实践,绍承朱熹,而有所差分。朱熹认为,二程所讲的“性即理也”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性是人之所以得于天的理。他在注《中庸》“天命之谓性”时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人物之生,各得所赋的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是所谓的性。在朱熹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为形而上下的关系,转换为性与气,是“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41]。性既有形而上性,便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与理相似“性无形象、声臭之可形容也”。性具有“寂然至无”的特性。从体用而言,性体是“寂然不动”的,情用是“感而遂通”的。
朱熹依据《古文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分道心与人心,“道心者,天理也”[42],“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是无杂,惟一是终始不变,乃能允执厥中”[43]。道心全是天理,是四端四德的仁义礼智的善心。“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44],“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45]。但朱熹认为,简单地讲“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46]。上智的也不能无人欲,因此“人欲也未便是不好”。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船与舵的关系,“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柁,则去住在我”[47]。道心、人心只是一心,并非心外复有一心,理在人心谓之性,性得于天而具于心,理在心中,犹性在心中。
道心与人心的舵与船的关系,是由心性关系推导出的。其一,太极与阴阳关系。“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48]太极(性)是一,分阴阳为二,太极不离阴阳,二而一。“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其二,虚实辩证关系。“性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既虚又实,既实又虚。“性本是无,却是实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体却虚”。心为一物、似有影象,为一物体,其体又虚,性虚,却是实理,体现其辩证思维。这里所说心其体却虚,是指心的体用的心体而言。其三,动与所以动的关系。“问心之动,性之动,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49]心处在运动中,心的所以动是性。“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性理不动,心发用。其四,心性体用关系。“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犹如心为包子,性是包子的馅。性是心的所有的理,“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性体心用。其五,善恶关系。“心有善恶,性无不善。若论气质之性,亦有不善”。[50]尽管性善,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天命之性是天理,所以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和合,所以有不善。本心是善的,但后来做了许多不善的事,所以心有善恶。
退溪继承朱子性即理的思想。他说:“性即理也。则彼所谓五行之性,即此元、亨、利、贞之谓也。岂可谓彼无而此有之乎?”[51]人物各有其性,而无物无性,退溪在解释周敦颐“各一其性”时说,孔子讲“成之者性”,“各正性命”,孟子讲山性、水性等,性具有普遍性,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概念。性内在于心中。“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52]五常之性具于心中。性具心中,是性先动抑或心先动。“心之动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动即心之所以然也”。[53]性心的动不可分先后,“心非性,无因而为动,故不可谓心先动也;性非心,不能以自动,故不可谓性先动也”。心性的动,既互为动因,又互为动的所以然。退溪心性互动、互因是其理气互发说在心性论的贯彻,亦是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完整性的体现。这是对朱子“动处是心,动底是性”的修改,也与栗谷异。
退溪认为“夫理与气合而有心之名”[54,这是从构成论视阈规定心,但理气的性质不能不影响心的潜质和动能。他又细分心的不同层面:“以其本然之善,谓之良心;本有之善,谓之本心;纯一无伪而已,谓之赤子心;纯一无伪而能通达万变,谓之大人心;生于形气,谓之人心;原于性命,谓之道心。”[55]此“六心”各置图的不同位置,虽属道德意识范围,但是心的虚灵知觉的基础。心是思的器官,具知觉能力。“耳听皆有天则,而主之者心也”56,“知者,心之神明”[57]。心的知觉能力,亦可谓之神明,呈现为思维活动能力。心具万理,“盖人心虚灵不测,万理本具”[58]。心若虚灵不测,能动静万变,神化妙用,不失其则,就不会出偏差,不会被事物所蔽,不会被私意所囿。心作为神明升降之舍或精神力量,就其本然而言,无所谓善恶。心具有天人合一的普适性。“理气之合则为心,故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己之心即千万人之心,初无内外彼此之有异”。[59]内之一人之心,外之天地之心,一己之心与千万人之心,无有分别,通同为一。心具有能动性、贯通性、可入性、普遍性。
朱熹以道心为天理,或性命之正,合乎义理。退溪、栗谷继承朱子说,退溪认为道心是义理之心,固原于性命,是存天理、灭人欲而获得的。“遏人欲事,当属人心一边;存天理事,当属道心一边可也”。[60道心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或理想境界。退溪重道心、人心之别,栗谷则注意两者的联系。他说:“人心、道心非二心也。人心、道心既非二心,则四端七情亦非二情也。”61两者为一心。进而说:“朱子既曰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亦有人心矣,岂可尽谓之人欲乎?以此观之,则七情即人心、道心善恶之总名也。”[62七情是人心、道心善恶的通称。并非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善为道心、恶为人心。七情包含道心,若说只指人心,只说对了一半。肯定人心有善的层面。道心为义理之心,是至善的,圣人所具有人心,出于性命之正,为四德四端的心,为朱、退、栗所同。至于对道心的追根溯源及道心范围的规定,退溪的发展,而异于朱子。栗谷从道心、人心的联系方面,说明七情是道心、人心善恶的总名,与朱子、退溪有异,即朱、退重一而二,栗谷重二而一,即一分一合。使道心、人心之辨以达圆满。
栗谷重道心、人心的二而一,是基于对心性为一路的体认。“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太差乎?须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63]所谓一心而各有境界,是指心的寂然不动时为性的境界,感而遂通是情的境界,因所感而抽绎商量的境界。虽心性情意各有境界,但不能分二而为一。从此思维逻辑出发,认为“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决非二性,特就气质上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之性耳,性既一,则情岂二源乎?……若如退溪之说,则本然之性在东,气质之性在西,自东而出者谓之道心,自西而出者谓之人心,此岂理耶?”[64]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性,而不同意退溪分东西两性,而分出道心与人心。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这是其“气发理乘”逻辑思维的贯彻,而与退溪理气互发异趣。
艮斋在心性论上,绍承朱栗,批评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即理说,并以形象的话语阐明性心关系。其一,“性是理之真体”。之所以是真体,是因为“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65]。性是人禀于天理,所以人与尧舜一样无差异;其二,“性是至善之理,不容修。扬雄言修性,是揠苗也”[66]。因为“人性全善而无些子偏恶”[67]。“性理全善而无恶;其三,“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心犹阴阳,太极为阴阳之主,而反为阴阳之所运用”[68]。在艮斋的思维逻辑结构中,理与太极同位,性是太极之体即性是理的真体;其四,性为义理之性。“义理之性,性与义理只是一物,非有二体可分。气质之性,性与气质只是一物,非有二物可指也”[69]。性与义理为一物,性之本就具有仁义礼智的义理内涵。“仁义礼智,吾儒之所谓性,而异学之所谓障也”[70]。性是伦理道德价值;其五,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艮斋在《气质之性》中开列五条:“第一,理在气中曰本然之性,而亦曰气质之性。如阴阳太极,形色天性,成之者性”71];“第二,理为气囿曰气质之性”;“第三,气质之禀,亦曰气质之性”;“第四,形气之欲,亦曰气质之性”;“第五,单指躯命,亦曰气质之性”[72]。这五种情况,均为气质之性,这是对气质在不同情境下的概括和体认。从气质之性来源说,“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合理与气质而命之曰气质之性。按气质之性是形而下之器也,气之局也”[73]]。气质之性为形而下者,是栗谷“理通气局”的气局的表现。从本然、气质不离而言,“离了气质更无性”。本然之性离了气质之性就无着落和安顿,气质之性离了本然之性就无根据和指导。此五层面为艮斋对性的规定,由此而可明心性之关系。
艮斋言心,其一,心为气,非理。“心事阴阳之属,无非是气”[74接栗谷心为气说,心气之上是至善大全不偏的理,然心非理。“心合乎理,则心非是理,而理为心本明矣”。[75]他屡批陆王“心宗家”心即理说,并认为退溪讲心合理气。[76]为维护栗谷心为气说:“心必待操而后存,则心之非理明矣,此栗翁所谓圣贤只要人检束其气而后复其本性者,所以为儒门尊性之道也”[77]。气与心是必须待澄明和操存的,理、天理不须澄明与操存,所以心非理。这是对心的内涵、性质规定理论前提。其二,为天地立心。“人君当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君心正,则天心豫而庆祥集焉,君心不正,则天心不豫而灾害至焉,天人感应昭然可见也”。[78]所谓君心正与不正,艮斋说:“圣人之仁如天地生物之心,有教无类,仁民爱众……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于方寸之中,是以逼人欲而存天理也”。[79]通过遏人欲,存天理,使人心得以正。其三,心为身之主。“心固是一身之主,然其所以主乎一身者,以其静而涵浑然之天,动而循粲然之天,而有妙用耳”。[80]心的动静若能涵浑然和循粲然之天,便有妙用。心主之能运用是因为“心为主宰,以心之存主运用,必本于性也”[81]。心本于性,才有主宰的功能。其四,心本善。“心之本善,亦以其有觉而知性至善,有力而体性之善也,故谓之本善也”。[82]心之所以说为本善,是因为其有觉有力而能知和体性的善的缘故。若保持其本善之心,就要不断地奋力振作。其五,心统性情辨。“心统性请,统犹兼也……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愚窃谓:善恶者皆出于天,情皆出于心,故曰天是统善恶的而言曰心统性情者也。若必以将帅统率军兵之实迹拟之,则天何尝统率夫恶,而行其号令;恶何尝拥护夫天而从其指麾,心安有指麾夫理而行其节制,理安有退听于心而遵其金鼓也哉。”[83]艮斋认为应先确立其思维逻辑体系的宗旨,而来体认其语意,“《朱子语类》季通云:心统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统名。”统名与统兵的统,语意内涵异趣。统名是“心统性情,是兼包该贯之义……非以尊统卑之谓也。”[84不是将帅统兵的尊卑关系。“朱子论心性情之分曰:横渠云:‘包性情者也,此说最为稳当,据此则统只见统总之义,非以尊卑之辞也’”。这样心统性情是心兼包、统总性情。这就为其“性尊心卑”“性师心弟”,性体心用,心本性等话题奠定基础和理论前提,也构建了其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一致性。
艮斋提出了既形象又有创见的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等主张。艮斋对于性尊心卑与性师心弟均有专章论述。其一,性尊心卑。在《性尊心卑的据》中,他从孔子、子思、孟子到二程、朱熹、尤庵共9条证据,并加按语:“性尊心卑不其明乎!”“万古最尊是性”,“以尊性为入道之门”,“性居尊位,而心从而尊之,则为儒者之学也。心不尊性而自尊焉,则为异端之学矣”。[85]又引朱子铭:“尊德性,希圣学。心若自尊而不肯尊性者,决是异学规模”86。心不能自尊而不尊性,这便是异端之学。其二,性师心弟。“性师心弟四字,是仆所创然。‘六经’数十万言,无非发明此理,可一以贯之。中夜以思,不觉乐意自生,而有手舞足蹈之神矣”。[87]“六经”之言,就是发明性师心弟的道理。“愚于性师心弟,虽未之能焉,而其自信之笃,亦可谓云尔已矣。古有心师、经师语,亦以心之师性,经之载道而言也”。[88]自古以来,心师性,他笃信性师心弟的创见是正确无误的。其三,就心本性言,艮斋著《心本性说》,认为“昔尝与朋友讲论得心本性三字,今以之做骨子”[89]。他用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道德关系来证明,心以性为根本、本体。“愚所谓心本性一句……学者苟能以此意善观圣贤经传,则句句是心本性,篇篇是心本性”[90]。此三层面,构成艮斋既接着朱子、栗谷心性论讲,与退溪有异,而又有自己独创性的诠释,其譬喻的通俗性,更易为民众所接受。
三、朱熹、退溪、栗谷、艮斋工夫论的会通
工夫论是为升华理想人格和风范,实现道德情操崇高境界,主体通过修身养性、居敬持志、主一无适、克去私欲的工夫,而完善其理气论、心性论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
朱子非常注重居敬穷理的道德修养工夫。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91]两者相资互发。居敬是持己之道,主体内在涵养工夫;穷理是格致之道,主体外在即物穷理工夫。从内在居敬而言,朱子认为“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去处。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语最妙”[92]。其妙处就在于“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93],心性存与不存,就在于敬。朱熹规定敬的工夫的内涵及功能:其一,敬乃圣门纲领。“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94]。敬极其重要,具有圣门的纲领和操存涵养的重要方法的地位,因此讲“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其二,敬具万理。“敬则万理具在”。“敬则德聚,不敬则都散了”。敬能凝聚道德天理,故“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主体人存得敬,吾心清澈澄明,天理显著美好。“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95]。即“存天理,灭人欲”之意。其三,敬为专一谨畏。“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96]把心收敛起来,不放逸而“始终一事”,“只敬,则心便一”。心一而谨畏,谨畏而专一,专一“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其四,敬为克己诚敬。“问持敬与克己工夫。曰:敬是涵养操持不走作;克己则和根打拼了,教他尽净”。[97]诚为诚实、诚信,去许多伪。其五,持敬的表现形式。“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严格’,‘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98]外在表现与内在思虑,内外表里如一。其具体表现“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99]。这是持敬的要求,并把其落实到行为的实践中,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缘由。
退、栗、艮结合其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朱熹的持敬涵养工夫。退溪说:“尝论持敬工夫。先生曰:‘如某者朝暮之顷,或有神清气定底时节,俨然肃然,心体不待把提而自存,四肢不待羁束而自恭,谨意以为古人气象,好时必是如此。’”100在朝暮很短的时间内,精神清朗,心绪安定,庄重整肃,心体不等有意而为便自存,四肢不等约束而自恭敬,这便是古人的持敬气象。退溪认为持敬与格物都不容易,若能认知持敬工夫方法,就能理明心定,格物就可明察,应事而不心累。
持敬涵养的内涵与价值:其一,以敬为本而有体用。“夫子尝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夫以敬为本,而有四者之事,岂不是兼该于体用”。[101]本有根本、本体之义,与四者之事的用对言,“静而严肃,敬之体也;动而齐整,敬之用也”102]。持敬的动静体用对举,体静为本,用动为本的表现或作用,是对程朱“以居敬穷理两言为万世立大训”[103]的发挥。其二,敬则心清气定。“盖怠惰则欲炽情流,而不宴不息,惟能敬则心清气定,而可以安养调息,故人能知宴息,亦以敬而非以怠惰,则可与论敬之理矣”。[104]只有敬使其内心清明,情绪安定,安静地修身养性。其三,主敬专一。“思明思聪等事,合在一时,思一不思二之疑,此则切问也……但所云一事方思,虽有他事不暇思之,此亦心无二用,主一工夫”。[105]主一工夫,就是心无二用。主事是无事有事湛然安静、随事应变。其四,正衣冠一思虑。李宏仲问:“若程夫子所谓敬者,亦不过曰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不欺不慢而已。”退溪说:“盖其曰正衣冠,曰庄整齐肃,是以静言。然而动时,衣冠岂可不整,容止事物岂可不庄整齐肃乎。曰一思虑,曰不欺不慢,是以动言。然而静时,此人尤不可不主于一,本原之地,又岂容有一毫欺慢乎”[106]。正衣冠,一思虑均是敬的内外体现,正衣冠,庄整齐肃,是敬表现一种视听言动方面的自律方式。一思虑,不欺不慢是敬的精神价值的体现。其五,持敬涵养。在《李子粹语》中特编“《涵养》一节,朱子指出;惟平日庄敬涵养,为本领工夫一节,尤为警切”。持敬是讲明心中之理,永保天理;涵养是培养心性本原,养心中之理。退溪说:“是以君子之学,当此心未发之时,必主于敬而加存养工夫。当此心已发之际,亦必主于敬而加省察工夫,此敬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而通贯体用者也”。[107]“省察”是指随时随事体察心中的理,“存养”是对于心性本原的培养,与涵养有相同之义。心未发时,主敬存养工夫,使本体心性达到完善。心已发时,主敬省察工夫,察识物理、纠其偏失,事事中节,反馈即物穷理以明心中之理。
退溪以敬为本、主一无适、心清气定、持敬涵养、正衣冠、一思虑的工夫论,其宗旨是明天理、去私欲。他比喻为磨镜工夫,镜本明,被尘垢所蔽而不明,心中理本明,被私欲所蔽,通过其工夫论,去尘垢(私欲),恢复其明。完善其理想人格,实现道德理想境界。
栗谷编纂《圣学辑要》五卷,他在《进札》中说明其价值:“凡帝王为学之本末,为治之先后,明德之实效,新民之实迹,皆粗著其梗概,推微识大,因此明彼,则天下之道实出此”[108],其宗旨是“圣贤之学,不过修己治人而已。今辑《中庸》《大学》首章之说,实相表里,而修己治人之道,无不该尽”[109]。《圣学辑要》就是围绕其宗旨而把修己、正家、为政之道结合起来,体现其人间性、实践性、生活性。就修己工夫而言,栗谷从立志、收敛、穷理、诚实、矫气质、养气、正心、检身、恢德量、辅德、敦笃、功效等十二个方面加以阐发,可见其致广大而尽精微。栗谷认为,修己工夫,必以“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明乎善,力行以践其实,三者终身事业也”[110]。本立而道生,故从居敬其本讲起:其一,居敬主一。“朱子曰:敬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间断。故此章大要义敬为主焉”[111]。要实现圣门第一义的敬,就要主一无适。“主一无适,敬之要法,酬酢万变,敬之活法……盖静中主一无适,敬之体也,动中酬酢万变,而不失其主宰者,敬之用也。非敬则不可以止于止善,而于敬之中又有至善焉。静非枯木死灰,动不纷纷扰扰,而动静如一;体用不离者,乃敬之至善也”。[112]朱子曾把主敬时的义,行义便有敬,敬义夹持,内外透彻,称为活法。栗谷称要法和活法,体用不离,动静如一,内外贯通,必须寡欲,“敬,主一之谓,从事于敬,则可以寡欲至于诚矣”[113],才能达到止善境界。其二,敬为圣学的始终。“敬者,圣学之始终也。故朱子曰:‘持敬是穷理之本,未知者,非敬无以知’。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言敬为学之始也。朱子曰:‘已知者,非敬无以守’。程子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此言敬为学之终也。今取敬之为学之始者,置于穷理之前”。114]圣学的始终都在于敬,持敬是穷理之本与入道之始,非敬无以守已知之理,立敬义,为圣学之终。其三,敬体义用。“敬体义用,虽分内外,其实敬该夫义,直内之敬,敬义存心也,方外之义,敬以应事也。”[115]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体用一原,直内方外,都是敬,只是存心与应事的差分。之所以都要敬,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方外是方方正正,自将去做圣门工夫。敬义夹持,直接上达天德。其四,恒主诚敬。“学者须是恒主于敬,顷刻不忘,遇事主一,各止于当止,无事静坐时,若有念头之发,则必即省觉所念何事,若是恶念,即勇猛断绝,不留毫末苗脉”。[116]时刻不忘主敬,不断克去恶念私欲,毫末不留,若是善念,穷理不断,使其明亮,回复本心之善。“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人不能复其本心者,由有私邪为之蔽也,以敬为主,尽去私邪,则本体乃全敬,是用功之要。诚是收功之地,由敬而至诚矣”。如何达到诚,由敬的去私欲、邪念的遮蔽,以回复本心的天理。其五,穷理涵养。“居敬为穷理之本”。117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穷理工夫大要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118]。此三项穷理工夫,均是主体向外通过即物、事、人、读书,而穷尽理,体认形而上的理本体。穷理工夫能否做到明义理、别是非、处当否,需要由极高明的主体内在卓越的素质、水准、判断智慧,这必须通过涵养工夫。“敬守此心,涵养积久,则自当得力,所谓敬以涵养者,亦非他术,只是寂寂不起念虑,惺惺无少昏昧而已。”119敬守此心,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此心寂静没有一毫思虑,在寂静中知觉清醒不昧,万象森然。只要涵养积久,就能穷理而理明。其六,敬贯知行。问“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此言何谓?曰:敬者通贯知行之间,故涵养致知,皆用敬焉”[120]。涵养致知知行内外、主体客体、知行兼备,通贯如一,以完善理想人格。“用功之至,必有效验,故次之以功效,以尽知行兼备,表里如一,入乎圣域之状”。[121]由敬知行,而通达道德价值理想的“圣域”境界,也是其修己工夫所达到的最崇高、最华彩的功效。
艮斋“某自谓主程、朱、栗”[122]。其实工夫论,也继承退溪。其一,敬为圣门工夫,“学者用功,将如何而可以矫治气质,而复还其性,只有敬以就中而已。天下道理只中一字便括尽圣门工夫,只敬一字便说尽”。[123]变化、矫治气质而恢复本然之性,“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敬就中,便可括尽圣门工夫,说尽穷理道理。“朱子曰:‘圣人只理会一个敬字。’……性以敬知性,以敬尽,只一敬而已。”[124]敬之价值与意义,艮斋及其重视。其二,敬功至精至微。“敬功至于无亏阙,无动摇,至精至微,至正至方,时时渊莹,处处圆融,方是尽处。若仅取一番操持,瞥然有主时便谓之敬,恐少间己,不可恃矣”[125]。敬的工夫,要做到无缺无动摇,精微方正,渊莹圆融,才是敬工夫的尽处,不是操持一番就可以的,要坚持不懈地去用功;其三,敬为北斗。“敬者,心之所以为主宰也。只言心则只是虚灵精妙之气耳。著个敬字工夫,如舟在大洋中不辨方向,而仰见北斗,始有子午可指。心而无敬便放倒,无复可以承夫理而宰乎身者也。”[126]心为气,心如大洋中的船,它不辨方向,敬如北斗,北斗指示方向,才能使大洋中船到达目的地,敬是心的主宰。“敬字工夫至则此心有事时,洞然外达。无事时,卓然中立。动而不累于物,静而不沦于空,此是敬功至妙处,然极难得力。”[127]“窃观圣人只一心敬,而万务皆叙。我辈学者只一舌敬,而百体皆肆,是所谓言行不相副也。”[128]圣人诚心为敬,万般事务都能澄明,若口头讲敬,放肆行为,便犯言行不副的病症;其四,敬则道凝。“敬则道凝而德成,不敬则道亏而德败,圣人聪明睿智,故自然能敬……今我辈学者,须勉强于敬功,时时处处必靠著敬字以为骨子。”[129]敬作为道德价值的凝聚与亏损,直接关系道德价值的成败,从这个意义说,敬是主心骨。其五,诚敬为万善骨子。“诚敬二字,吾儒以之为万善骨子……朱先生教门人云:学者之心,大凡当以诚敬为主。”[130]批评心宗学者如陆九渊等不以诚敬为主的偏颇。诚敬之所以是万善骨子,是因为“敬以明理,诚以从道,此两句工夫尽时,已是换凡骨以接圣脉。”[131]敬诚的价值在明理从道,此工夫做尽,就能脱凡骨换圣脉的转生。其六,敬贯知行。“学问之道有四,格致、存养、省察、力行,而存养贯始终,此晦翁敬贯知行之说也。”[132]“敬皆包得知行在内,不可一时一事不用诚敬也。余每谓有意时诚行焉,无意时诚立矣,格致时敬行焉,诚正时敬立矣。”人不可须臾离开诚敬,时时事事要用诚敬,格物致知是敬的行为,诚意正心是敬的确立。敬贯知行,需通过存养、省察工夫,如“庄敬整齐以自持于言动事为之间。”[133]“学者工夫,只有操心治气,以顺其性一事而已,”[134]以达存天理,去私欲的境界。艮斋工夫论以敬为核心话题,与退溪、栗谷会通,而有所发挥,以敬为北斗,为指针。
四、朱熹、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精神的特质
朝鲜朱子学的双璧退溪和栗谷生活在燕山君与宣祖时代,当时天灾频仍,经济凋敝,人祸迭起,生灵涂炭。执政者内部斗争激烈,往往与“士祸”相终始,使诸多性理学家遭受杀身之祸。艮斋生活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为日本侵略者占据的时期,他誓死与其不共戴天。退、栗、艮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济民的悲愿,以自己终生的忧患去担当忧道、忧国、忧民的大任,以自己民族大义的思想精神感召大众去实现“天理”的人间世。他们的思想精神特色是:
其一,义理精神。性理学家以求理为宗旨,以存天理为目标,以居敬、涵养、知行为工夫,在国家危机、民族灾难之际,为挺立民族脊梁而弘扬义理精神,为忧国忧民、经世济民而担当历史使命,成为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精神与实践活动的核心内涵,体现了其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退溪在《戊辰六条疏》中的第一条就是“重继统以全仁孝”。孝为百行之原,仁为万善之长,一行有亏与一善不备,就不能全仁孝。第三条为敦圣学以立治本。帝王和常人都应以“敬以为本,而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为原则。第四条明道义以正人心,都凸显了其义理精神。退溪和栗谷义理精神表现在对四次“士祸”的忧患上,认为有损国脉,有害社会正义。他们痛心疾首,忧患再次发生“士祸”。因而提倡圣人之学,退溪造《圣学十图》,栗谷编纂《圣学辑要》,从圣学的各个层面,为性理学的义理精神规划了理气观、心性论、工夫论的内涵、性质的方向和实践活动的路径。艮斋在辱权丧国的患难中,坚守民族义理精神和礼仪大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变服、断发令。他决不“牵制于仇虏之手……窃以为中正之道也”[135],后决意“入海守道,讲明大义,以扶缐阳于既坠”[136]。这是弘性理学义理精神,扬民族中正大义精神。
其二,敬诚精神。性理学家道德理想的实践,修身养性的实现,道德情操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完善,都需要通过敬诚的多方面不断培育,以达人生最高境界。退溪、栗谷、艮斋弘扬朱子理体学,“朱熹自少有志于圣道,为其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137]。从经旨不明,道统之传昏暗,朱子竭其精力研究穷尽圣贤的经典古训,他所著的书为学者所宗。退溪以敬为本而有体用,主一无适,持敬涵养,心清气定,反躬践其正衣冠,一思虑,以去私欲明天理。栗谷提倡敬是圣学的始终,主一主事于敬,便可以寡欲而至于诚。恒主诚敬,发扬善念,断绝恶念。居敬以穷理为本,由敬而至于诚,只要涵养积久,就能穷理而理明,存养知行,都需要敬,因为敬贯知行之间,而彰显躬身实践诚敬的功效,而达道德价值理想的“圣域”境界。艮斋以圣门工夫敬可说尽,敬是北斗、指南针,是航行于大洋中不迷失方向的子午。敬至精至微,渊莹圆融,圣人诚心为敬,万般事务澄明,诚敬是人的主心骨,它是万善的骨子,人须臾不离诚敬,从不间断,无所不贯,贯通知行。诚敬为立本的工夫,本立而达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理想境界。
其三,创新精神。退溪、栗谷、艮斋在义理、诚敬精神的大本大志、大是大非的地基上,建起了其新性理学的大厦,其间创新是新大厦之所以新之所在,是新之所新的生命和灵魂。创新是既继承又超越,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新瓶装新酒。在理气观上,退溪着眼于朱子理的“三无”说,而化解被曹端所质疑的困境,主张理自会运动说,“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生气也”[138]。因而“四端七情”之辨中主理气互发说,这是对理的动静的创新。栗谷的“理气妙合”和“理通气局”说,亦是对朱子理气观的发展和创新,他们既赋予理气观以新生命,也是朱子理气观转生为朝鲜朝理气观的实现,换言之,退溪、栗谷的理气观是转生朝鲜朝朱子学的关键节点。由理气观而推致心性论,退溪认为理气合有心之名,并将心细分为六层面,对道心、人心之辨的追根溯源和道心范围的规定是其发展。栗谷重道心、人心的二而一,圆融无碍。艮斋提出“心本性”“性尊心卑”。
“性师心弟”说是对朱熹、退溪、栗谷心性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论思维逻辑的创新是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精神价值所在,唯有创新才能生生不息,唯有发展才能完善朝鲜朱子学——朝鲜性理学,使之永垂不朽。
其四,逻辑精神。这里是指其理论思维体系的概念范畴的逻辑结构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或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哲学思想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哲学思想概念范畴按逻辑顺序或结合方式构成的,并从整体的逻辑结构上,确定诸概念范畴在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就是说哲学思想史作为观念逻辑的演变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概念范畴发展史。就本文所论之理、气、心、性、敬、诚等概念范畴而言,各哲学家其概念范畴在其哲学思想逻辑结构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正说明不同概念范畴在其哲学逻辑结构体系中的差分,如退溪主理,栗谷主气,艮斋讲性尊心卑、性师心弟,为其明证。又如退溪《圣学十图》、栗谷的《圣学辑要·目录图》、艮斋的《命性图》等,每图都将其最高的核心概念范畴置于图式的最高位置,对整图有统摄意义和价值。他们都曾以图式的形式来表现其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体系,每造一图都是他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精华所在。退溪的《圣学十图》是:“或抽绎玩味于夜气清明之时,或体验栽培于日用酬酢之际,其初犹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时有极辛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谓将大进之几,亦为好消息之端。”[139]可体会其为造《圣学十图》的殚精竭虑的心得,是从日夜辛苦中得来。栗谷的《圣学辑要》是“深探广搜,採掇精英,汇分次第,删繁就要,沈潜玩味,反复櫽括”[140],反复剪裁改写、取其精华而成的,其得来不易。艮斋的《命性图》是与“湖中士友相与虚怀讲究,而解此迷蒙,实平生切愿尔”[141]所完成的。这些图式化的概念范畴逻辑结构,是其概念范畴运动形式以及各概念范畴之间相对稳定的排列顺序或结合方式,它是各概念范畴逻辑结构内各个层次、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作用总和的表现方式和逻辑思维的形式。
其五,笃行精神。学问思辨,逻辑思维、理气心性、价值观念,都要落实到行上,无笃行,理论思维是空虚、是无生命力的,也不会持久和生生不息。退溪认为居敬要落实到实际行为之中,如正衣冠、一思虑,庄整齐肃,并落实到家道、家规上。“凡为子孙,当谨守家法。”142]如果任意忘礼,废三世家规,这是很严重的事故。栗谷所规划的修己正家为政之道,把正家落实到孝敬、刑内、教子、亲亲、谨严、节俭上;为政落实到用贤、取善、识务、法先王、谨天戒、立纪纲、安民、明教上143],都是讲日用之学。艮斋认为居敬、涵养、省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言行一致,在《家规》中规定得很仔细,从孝敬、守家礼到冠婚丧祭礼的实行,以及女子必令读女戒女范等无所不及。在《蓍洞书社仪》中规定“就座展卷,端庄肃敬,如对圣贤、从容诵读,仔细究索,不得与人说话,不得无事出入”144。在《凤寺山房规约》中规定“读书须整襟端坐,正置册子,专心诵念,勿高声,勿摇身,少顷掩卷思绎,务令指意分明,义理浃洽”[145]。退溪、栗谷、艮斋都是以身作则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实践家、思想家、哲学家。正是这种笃行精神,使其思想精神在现实中光彩夺目,为人所敬仰,为后世所高山仰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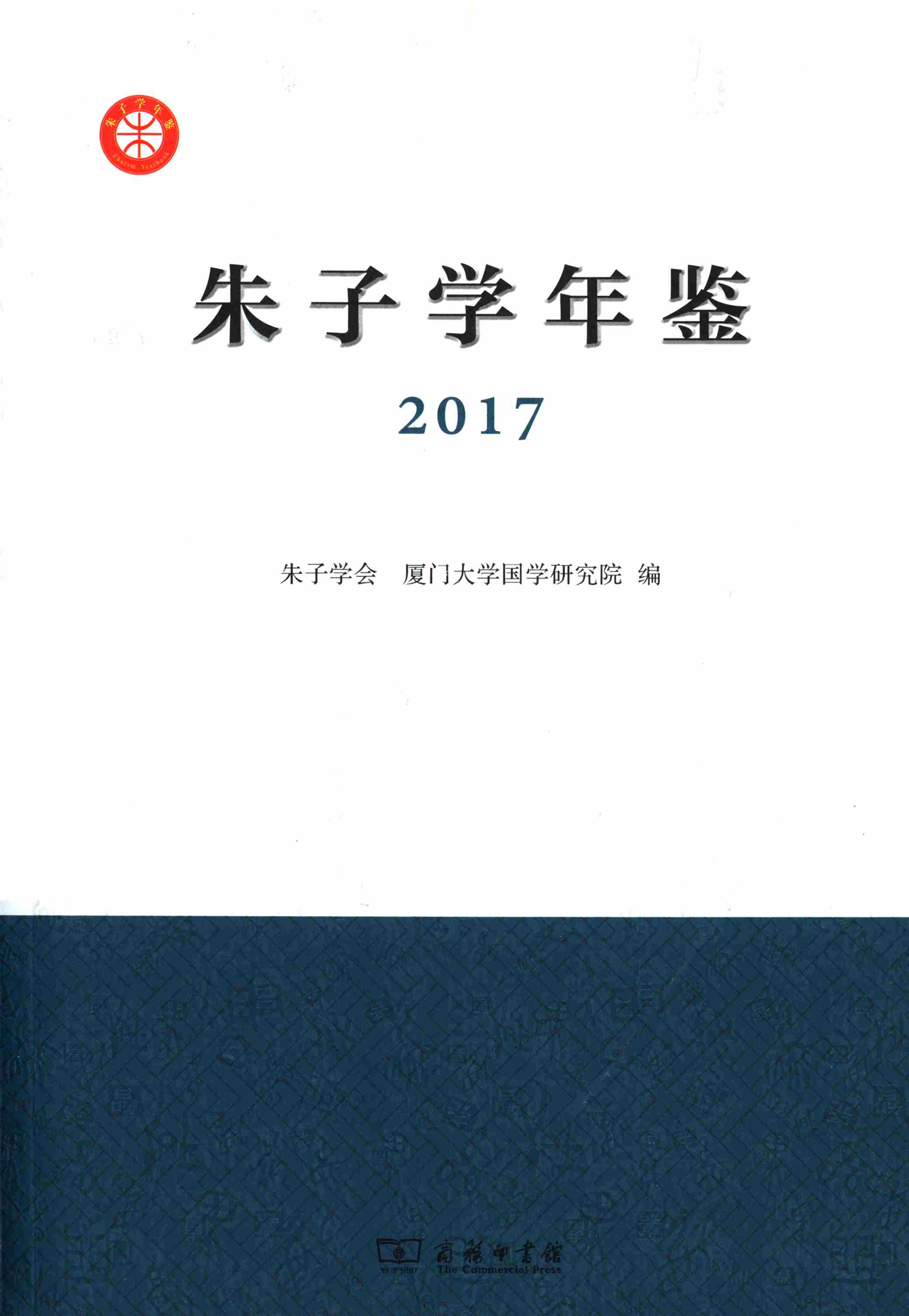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7》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仁者人也”新解》《朱子学的构建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朱熹与陈亮往来书信编年考证》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张立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