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7》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102 |
| 颗粒名称: | 特稿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9 |
| 页码: | 001-019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特稿包含“仁者人也”新解、朱熹论“人心”与“道心”等介绍。 |
| 关键词: | 朱子学 仁者 朱熹 |
内容
“仁者人也”新解
陈来
在儒家哲学中,“人”与“仁”可互为定义,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孟子所说的“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也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也是先秦儒学对“仁”的唯一定义式的表达,从秦汉到宋明,儒家学者对之做了各种解释,在现代儒学中仍然受到重视。本文就此命题及其意义进行一些讨论,以扩大分析这一问题的哲学视野。
关于“仁也者人也”这一命题,古代文献中出现了三次,并且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解释,本文则突出第三种解释的可能和意义,并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中予以强调。
一、人能亲爱施恩说
“仁也者人也”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此后又两见于《礼记》。以下我们先举出这三个材料,以供读者参考。
1.《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孟子》一书的注释,最早为汉代的赵岐,赵岐注对此的注释是: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2]仁的本义虽然可以解释为仁恩,即对他人实行恩惠,但“能行仁恩”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里的“人也”,因为不仅能行仁恩者是人,能行其他德行者也是人。
正如与这个命题的形式相同者:“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3]],其解释方法,都是要用后面的字训解前面的字,如用“宜”训解“义”,用履训解礼,用知训解智,用实训解信。按此思路,“仁者人也”应是用人来训解仁,换言之,是强调仁与人的关联,而这在赵注中却无法体现。赵注只有在孟子原文是“仁者恩也”的条件下,他的解释才能与之相合。可见赵注的注释在说明仁和人的关联上并不能令人信服。
2.《礼记》第31卷《中庸》20章: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4]
对此,《礼记正义》引述了郑玄的解释及孔颖达疏的发挥:
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疏云: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者,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〇“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宜,谓于事得宜,即是其义,故云“义者宜也”。若欲于事得宜,莫过尊贤,故云“尊贤为大”。[5]
这里是用“亲偶”解释“人也”,亲偶也就是人与人相互亲爱。仁就是去亲爱你亲爱的人。这种用亲偶解释仁、人,在先秦是没有的,也是不清楚的。可见汉儒及其影响下的解释,其实都是以仁的相亲爱的意义延伸解释的。
3.《礼记》第32卷《表记》: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礼记正义引郑注:人也,谓施以人恩也。疏云:“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爱偶也。〇“道者义也”,义,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断割得宜,然后可履蹈,故云“道者义也”。
正义:“人也,谓施以人恩也”,解经中“仁者人也”。仁,谓施以人恩,言施人以恩,正谓意相爱偶人也。云“义也,谓断以事宜也”,谓裁断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义也”。[6]
这种解释在方向上是与赵岐《孟子注》一致的,用施以人恩来解释“仁者人也”,所不同的是把仁恩与“相爱偶”结合一起,与郑玄接近。但这里对“仁者人也”的解释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无论如何,从以上已经可以看出,“仁者人也”的命题,其实并不是给“仁”下的定义,而是要强调仁与人的关联性,而如何阐明此种关联性,成为儒学史的一个课题。
二、人之所以为人说
宋代理学兴起,理学注重的是经典的思想诠释,与汉儒注重字义训诂不同。对“仁者人也”的义理解释先见于张载。《宋元学案》卷十八:
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7]
这里初步提出了“仁者人也”的“人”应解释为“所以为人”,即仁是所以为人者,这种对仁与人的关联性的说明,较汉儒为合理。
“所以为人”即是人的本质。最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完整提出了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说。朱子《孟子集注》尽心章: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8]
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然未详其是否也。[9]按照朱子的解释,“仁者人也”,其中的“仁”指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其中的“人”是指人身而言。整句是说仁作为人之理具于人之身上。其中既体现了朱子的道德意识,也体现了朱子的身体意识。
朱子《中庸章句》: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为政在人,家语作“为政在于得人”,语意尤备。人,谓贤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10]
这里提出“仁”是天地之心,也是人得以生的生理;“人”是人身,人身是具此生理的主体。
《朱子语类》中记载的朱子与学生有关孟子“仁也者人也章”的讨论有不少,这些语录进一步发挥了朱子《孟子集注》和《中庸章句》的思想: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间,浑然天理,动容周旋,造次颠沛,不可违也。一违,则私欲间乎其间,为不仁矣。虽曰二物,其实一理。盖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11]
这是说“仁者人也”是讲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说,仁是人的本质。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说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体认出来。又就人身上说,合而言之便是道也。[12]这是说仁是人之理,又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仁者人也”。人之理就是人的本质、本性。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与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犹
言“公而以人体之便是仁”也。[13总之,“仁”与“人”要互相定义,彼此不能离开,“仁”不能离开“人”去理解,“人”也不能离开“仁”去理解,必须合而言之。人是仁所依存的主体,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训仁。且如君臣之义,君臣便是人,义便是
仁;尽君臣之义即是道,所谓“合而言之”者也。[4]照朱子这个说法,“仁者人也”并不是声训之法,与“义者宜也”不同,是讲人和理义的关系,人是伦理关系的主体,理义是伦理关系的规范,仁则是理义的代表。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则不见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见得道理出来。”[15]
问:“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说仁不说人,则此道理安顿何处?只说人不说仁,则人者特一块血肉耳。必合将来说,乃是道也。”[16
这两段也是说,为什么要说仁者人也,因为讲到仁而不涉及人,则作为人之理的仁就无处寄寓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讲人而不涉及仁,人与仁、理都无关系,这样的人没有道德本性而只是血肉而已。这是朱子发挥其“理在物中”的思想来解说《孟子》的文句。
问:“先生谓外国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据?”曰:“向见尤延之说,高丽本如此。”[17]这是对《孟子集注》中“外国本”的询问,朱子的友人尤延之看到的高丽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还有对义、礼、智、信的训解,比较全面,可惜此本未传。
问:“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别物,即是这人底道理。将这仁与人合,便是道。程子谓此犹‘率性之谓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对‘义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说‘仁’字又密。止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说‘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统而言之。”淳。[18]
这是说,《中庸》的“仁者人也”,人是人身,仁是生意,强调在人身上的生生之意。这显然不是训诂的解释,而是哲学的解释。
综上来看,朱子的解释是,“仁者人也”首先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这一解释与汉儒解释不同,突出了仁与人的关系;但需要把“人”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略为曲折。其次,“人也”是强调仁具于人身,体现于人身,人身是主体。可以说朱子注孟子是哲学的诠释,不是训诂的解释,强调“仁者人也”是指仁是人的本质、人的标准。换言之,朱子认为,仁必须关联着人来定义,因为仁就是人的本质、人之理,所以孟子强调“仁者人也”。
不过,朱子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强调“人者仁也”,用仁去定义人的本质。这与“仁者人也”有所不同,因为“仁”是定名,“人之所以为人”则是不定之名,用不定之名解说仁,其意涵并没有确定。
在明代的学者中也仍有用生意发挥“仁者人也”的意旨,如《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二:
仁,生机也,己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礼则物之则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则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机?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于克己复礼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则,斯有所间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虽其一身生机,亦不贯彻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礼勿视,目得其则矣;非礼勿听,耳得其则矣;非礼勿言,口得其则矣;非礼勿动,四肢得其则矣。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则,则吾一身无往非生机之所贯彻,其有不与天地万物相流通者乎?生机与天地万物相流通,则天地万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归仁”。[19
这是说仁是生机,所谓“仁者人也”是说人的身体处处体现仁的生机,与上引朱子之说相近。很明显,宋代以后对“人也”的解释都不离开身体的意识,把身体意识与仁结合起来。
三、人指他人说
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20]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21]宋以来一般认为,这是强调仁作为人道的根本原理,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其实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即我们也可以说,“仁者人也”是指“仁”包含了他人优先的伦理原理,以下我们就来说明这一点。
《中庸》中对仁的理解,与《孟子》的“仁者人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一致,强调仁作为人道的根本原理,而仁的原理的实践,以亲亲为根本。如果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还不能简明地概括仁和义的要义,《礼记》的另一个说法“仁以爱之,义以正之”[22],则清楚地把仁和义的要义阐明了,仁的要义是慈爱,义的要义是规范。《礼记·表记》:“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这也是继续强调仁所具有的“亲而不尊”的特点,也点明了义“尊而不亲”的特点。亲亲本来是子女对父母的亲爱,孔门后学则把亲进一步扩大,如《礼记·经解》中的“上下相亲,谓之仁”,也就是发展了仁的相亲的含义,从伦理的亲爱推及于政治社会的人际关系。
仁者人也,可以说是采取一种声训的形式,即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但《孟子》《中庸》的“仁者人也”的说法,并不完全是训诂,而且还是将之作为一种表达一定哲学思想的形式。其实,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说文解字》的解释“仁,亲也”是和郑玄的《礼记注》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不能解释“人也”二字。宋儒把“人也”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也还是曲折了,不太可能是先秦儒的本义。现代训诂学也接受了宋儒的说法,其实,并不一定要采取这种过分哲学化的诠释。
若分析起来,有一个简易的训诂意义被宋以来的儒学忽略了,即“人也”的“人”是“人我”之人,即指“他人”。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汉代儒学的仁学如果说有何贡献的话,应该说主要表达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在《礼记·乐记篇》中曾提出“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但并没有说明爱和正的对象。而《春秋繁露》最集中表达的是,“仁者爱人、义者正我”,在仁义的不同对象的对比中阐释他们各自的意义。董仲舒提出: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23]
与《荀子·子道篇》“仁者自爱”说不同,董仲舒明确主张,“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认为一切道德无非是对他人或对自我而言的,“仁者人也”的意思,就是着眼于他人,仁是仁爱他人的德行;相对于仁者人也,则是“义者我也”,表示义是纠正自己的德行。仁作为“爱”是爱他人,不是爱自己;义作为“正”是正自我,不是正他人。这个对比的说法是先秦儒学其他各派中所没有的。他认为,自爱而不爱人,这不是仁。仁的实践必须是他者取向的,义的实践则必须是自我取向的。可见,董仲舒对仁义的讨论,重点不是价值上的定义,而是实践的对象,是密切联系着仁的实践的。董仲舒对“仁”与“人”的关联诠释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伦理意义,此即他者的人道主义,这一点以前都被忽略了。近人梁启超也说:“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常在我也。”[24]也是把“仁者人也”的人理解为人我之人。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解释,儒家的伦理是尊重对方的为他之学,而非为己,为他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在梁漱溟表述的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伦理正是列维纳斯所谓的“他者的人道主义”而不是“自我的人道主义”。
在某一个方面来看,仁正是如此。在伦理上,仁不是自我中心的。宋明儒学喜欢讲儒学就是为己之学,这仅就儒学强调个人修身的方面来说是不错的,儒家讲“克己”,讲“古之学者为己”,都是这方面的表现。但是儒学并不能完全归结为为己之学。仁的伦理意义和修身意义是不同的,伦理的仁指向他人,修身的仁指向自我,这是要分别清楚的。孔子仁学中总是有两方面,克己和爱人是这样,修己和治人也是这样。“内圣外王”的说法虽然最早出于《庄子》书中,宋明理学家也不常用这个概念,但孔子讲的修己治人与内圣外王相通。故孔子以来儒学本来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而仁学不仅是克己,更是爱人,不仅是为己,也是为他,这在汉儒对仁的伦理界定看得最为清楚,也是汉儒的贡献。所以,直到唐代的韩愈仍然以汉儒为出发点,以博爱论仁,博爱指向的正是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我们的诠释,孟子所说“仁者人也”中的“人”字亦即是“他人”之意,是人己之人,是人我之人。董仲舒是最先肯定这一点的儒学家,“仁之为言人也”这一思想虽然并不是在对《孟子》或《中庸》“仁者人也”的注解或诠释中提出来的,但实可以作为“仁者人也”的一种理解和解释。在事实的层面,我们看到很多能克己的人却不一定能尊重他者、亲爱他者。因此,做人与为仁,既要克己修身,又要爱人亲民;做人与求仁不仅要去除私欲,严谨修身,还要克服自我中心,以他者为优先;做人与践仁不仅体现在对控制欲望的自我修养上,也体现在如何对待他者、他性,如何体现恕道,这是以往较受忽视的地方。今天我们重提“做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仁者人也”这一问题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一个文本根据不同理解可有不同意义,文本的意义可以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视界融合而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对“仁者人也”的三种理解而言,无须以其中一种去彻底否定其余两种,而应该承认这些理解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思维,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人们对儒学仁论或人论的理解。
四、仁者人也的现代诠释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怎样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呢?
1.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法意味着这些价值的适用性不仅在一个国家之内,更适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和关系。简言之,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更是指适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应是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故也可称为“世界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提出,是把原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价值“世界化”,以构建合理的世界秩序。
关于基本价值的世界化、国际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自由、公平是20世纪西方世界特别重视的价值。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奉行民主、自由、公平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他们并不是“普适”的,只是其国内的政治价值,不是世界的价值。在世界事务中他们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公平即主张各个国家一律平等,民主即世界大事要共同商量,反对大、强、富国欺压小、弱、贫的国家。人类共同价值是要把这些价值真正扩展到人类所有事务,使之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价值。
2.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伦理”运动。世界伦理又称全球伦理,在我看来二者略有区别,世界伦理可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的行为准则,而全球伦理则指跨文明的人类行为准则。这就引出一个讨论,“世界伦理”是不是“人类共同价值”?从被一致公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看,应该说世界伦理即是一种价值观,也是谋求确定人类基本的价值共识,全球伦理就是要展示人类基本价值和道德。因此,“世界伦理”应当属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伦理基础。区别在于,世界伦理的指向,是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然不限于个人),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以国家为单位,指向国际关系,并不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别对应三个层次,即个人、社会、国家,而“人类共同价值”则针对在“国家”之上,是第四个层次,是国家之间的世界。这就使我们对价值的认识形成四个层次,世界、国家、社会、个人,更为完整。
然而,真正确立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之间的世界政治层面。我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必有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世界伦理。没有世界伦理,特别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共同价值就不完全,就缺乏道德的基础,也就不能找到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关系角度。
3.有了伦理道德基础的角度和视野,我们就能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关系。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应该说表达了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总体而言,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分而言之: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是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第四,“以德服人”,王道正直,是“和平”的基础;第五,“天下为公”,不以私利为原则,是“正义”的基础(如全球气候问题及其义务分配)。
这五项不仅可以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成为这些价值后面的深层理念,它们本身也是人类生活最基础的道德价值。故人类共同价值除了世界事务、国家间关系的价值约束外,也同时是人类一切生活所必需。由此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原理的普遍意义。
其实,上述五点都是儒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这也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仁”与“人”的关系,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对“仁者人也”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诠释,即“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或“仁是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原理”。
(论文前三部分载于《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朱熹论“人心”与“道心”
——从心的主体化与主宰性到道德心的实践
﹝美〕成中英
一
朱子曾讨论“人心”与“道心”的差别,并涉及了“人心”如何能实现“道心”这一命题。通过围绕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可以凸显朱子心性之学的特点与得失。首先有必要回溯朱子对“心”的认识以展开讨论。朱子对“心”的认识,有其包含性与深刻性。他既整合了两宋理学家对“心”的认识,又重新系统而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所涉及的“心”之概念的含义。
1971年,笔者曾撰文论述中国古典儒学中“心”的概念,指出:《中庸》着重探讨了“性”的问题,多次举“性”字发论,辨析“性”的功用,但罕有对“心”的说明,至少没有明显地论述“心”;《大学》探讨了“心”,但对“性”的论述则较少。在《孟子》处,既谈了“心”,也谈了“性”,且此二者在孟子看来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有道德感情,发而为四端,四端皆可谓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这里的四端之“心”,均直接指向一种“心”的活动,其又能用来说明人的“性”之为善。因此,在早期儒家学说中有这样一种古典的论述:“心”是“性”的表达。[1]
到了宋代,胡宏对这种古典的论述有了新的表达,认为“性”是体,“心”是用。不过,朱子对此又有别样的认识。朱子的看法,既结合了张载、二程的学术传统,又体现了人的直觉经验,故而有了新的认识。他的看法至少应该被认为包含了以下两点:(一)“心”就是知觉,人所谓有“心”,也就是有知觉能力,张载和二程也均做了类似的肯定(而佛学中的“五蕴”也是在说明“心”的知觉或感觉之能力);(二)“心”是一种主宰,它“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2],此说大抵在他近40岁时与张栻论学后才整合得出,是他处理“心统性情”之提法的重要认识前提。对于“心”作为主宰这一思想的根源,吾人可以追溯至荀子处。在《解蔽篇》中荀子明白地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3]这里强调了“心”自主活动的能力,即属于彰显“心”之主宰性的说法。所谓“心”能作为主宰,一方面表明其有自我控制、自我确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指它能影响与其有关的性情,即朱子所发扬的张载的“心统性情”说。
至此,吾人应该分析“心”与“性”的关系。首先,“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特质与潜能。古典儒家很早就重视“性”这一概念,孔子即强调“性相近,习相远”[4]],又说“人之生也直”,这里的“生”与“性”是相互联系的,“生”的表现就是“性”的表现。孔子以“直”训“生”,一方面能表“直接”义,也就是说,兹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表现,其并非是在曲折地表达某些不可知的东西,而是在直接地显明其特质;另一方面,“直”又可能带有道德含义,也可被训为“正直”。事实上,“直”是“德(悳)”字的一部分,本身可能就具有好、善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本是趋向于善的,并以趋向于善为善。从宇宙论的角度看,人之生命的出现,更可以被视为是“善”的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生”就是“善”的,生生不已的发挥、发展也是“善”的,“善”亦自与“生”相关联。因此,《易传》乃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5]]。能继承生命的本源,并将其发挥下来,持续地发展其内在的能力、表达其内具的德性,这就是“性”,而从其根源上讲,这又是“善”。这就是古典儒家从孔子到《易传》对“性”所具有的深刻体验。
而“性”也可以被表达出来。当其未发之时,还处在一种内在的状态。“性”的内在性和它的外在性(表达性),存在着一种从未发到已发的对立。以《中庸》言之,若其已发,则即发为“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犹然是和自然“性”相关的,那么,自然“性”如何与道德“性”建立关联、形成转化,就尚需要深刻的分析与探讨了。对此,朱熹将“性”的表现称之为“情”,同时,在注解《孟子》时,他又将“恻隐之心”的“心”训为“情”。他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6]广义的“心”应该包括知觉力与主宰性,但对于《中庸》所说的“未发”而言,这种“未发”究竟是“性”之未发还是“心”之未发,仍是值得讨论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即便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心”与“性”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难以割裂。以我观之,“心”是“性”的一种流露,而这种流露又以“情”的方式得以外在表现。“喜怒哀乐”既然能“发”,当然是“情”;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朱子认为也是“情”。这种“情”,是道德之“性”的基础,故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作为“情”的四端之心,表达的是一种“性”的真实不虚,是一种道德、价值与伦理。而这种“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必须被实现出来,且必须随时能被实现出来。当然,具体如何才能把“性”之本然具有的内在之德,实现为表达此道德之“性”的“情”,其中的理路在朱子与其他古代儒者那里,其实是有扦格与跳跃的。
除了“情”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考虑“意”这一范畴。之所以要在“情”外更讲“意”,是因为存在一类意向性的问题。“情”如果不能展现为“意”,就不能成为行为的基础。因此,“情”尚不是最向外的一环,其更为外发则应归为“意”。所谓“意”,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导向与动力。
那么,在将“意”也考虑在内后,“心”究竟是什么呢?朱子在注“四书”时,实际上已经对“心统性情”这一说法有了深刻的了解。这和他的“中和新说”有密切关系。他扭转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传统中可以说,“性”是从“心”里开展出“情”,继而可再说从“情”里开展出“意”。朱子则以“心统性情”的方式调和了几个范畴间的关系。“心”除了有知觉力与主宰性外,还有一种理性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单纯的知觉力相区别的。“心统性情”这一命题,在彰显“心”的理性认知、价值判断方面,尚有未尽,但在高扬“心”的统帅能力处,则非常透彻,足以体现朱子对“心”有着认识深刻的一面。不过,这样也改变了某种对“心”“性”之间内在结构的认识。
依照古典儒学的观点,“性”后有“心”,没有此“性”就没有此“心”,比如,“恻隐”之心等四端,均是基于“性”而能发的。在这个意义上,“性”才是本,而“心”是可被摄入“性”之中并逐渐自然觉醒开发出来的。这确是人的特点。很多动物并不可谓有“心”的概念,它们只有本能,只有动物性,而决不可谓有“心”。究其原因,在于动物虽有知觉,但无主宰。它们都可以被条件化,故不能说有主宰。对于外部的世界,它们更不可能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只是基于本能而为满足欲望做出觅食等事罢了。因此,也不可说动物有一种“理”的自觉,仅是处在“气”的运行之中而已,这也是判定其不可言“心”的理由之一。所以,“心”似乎确应作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
朱子的观点则与此不同。通过整合先秦儒者与二程的观点,他实际上有着如下这样的理路。“心”在从“性”中发展出来后,自觉为“心”,本是“性”的一部分,比如《性自命出》里就提到了人虽有性但心无定志的问题,孔子也说“从心所欲”,在这个意义上,心是有其来去无定之自由活动性的。“从心所欲”之所以能“不逾矩”,是因为其“性”在匡正着“心”,于此,“性”规定了“心”的活动范围,在“心”与“性”直接,“性”仍是主动的。在这里,透过一定的自觉修持,“性”具有一种潜力,可以约束随时发生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实则是一种以“心”为主体的欲望。这种欲望可以是身体的欲望,但其毕竟又透过“心”的方式得到自觉的表达。换言之,一旦有了自觉的意识,就有了“心”的存在。这就使“心”作为主体而存在,将“性”的主体性转化成了“心”的主宰性。
作为一个主体,“心”固然是源于“性”的,但若以我所常用的“本体”概念观之,则能清楚地厘清两者的关系。“性”是一个“体”,可谓之性体。此性体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内里涵有一些表达与行为的活动能力。而这种能力有一定的方式、方向,具备目的性。具有这样内涵的“性”,引起了一种自觉,即成为“心”,产生了一种“心”的主体性。所谓“心”的自觉,即是“心”能自己了解其自身,觉知其之所以存在为其自身,形成了自己的“体”。
“性”之本即是“理”,这个“理”,是天地之理。不过,“性”也是通过气质的存在来得以实现的,需要气质作为其载体。所以,宋明理学宇宙论的基础,即在于对“理”与“气”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是对外在之宇宙世界的观察,也建筑在人之存在的内在观察上。从外在观察即宇宙观察的角度看,人之为人,能看到天地之变化,能看到天地运行的规则,即《易传》所提到的观天察地之事。《易》认为人能在观察中掌握宇宙变化之道,乃据此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7],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易学哲学。因此,人的存在既有“气”的成分,也有“理”的成分。当二程说“性即理”的时候,就是指“性”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有着内在的价值。“性”同样也兼具“气”的成分与“理”的成分。就宇宙本体论而言,朱子也探讨了“性”与“理”的关系。朱子将两者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二元的关系,认为两者间是相互作用的。不过,从《朱子语类》第1卷中的表述看,他又认为“理”究竟是最终的存在。这与之前他理气相须的说法间即尚有需要调和之处。
既然朱子认为太极在其作为终极存在的意义上就是“理”,那么,“理”作为一个可等同于太极、涉及存在之本的范畴,就必然及于“气”。在这个意义上,创化之“理”又是“道”。这样一来,朱子认为太极只是“理”,便终究有自相矛盾之处,因其必然也是“气”。理气于此是合一的。只不过“理”“气”可分而被视为形式与质料、动力与目标罢了,但其终究是相互依存、不能分开的,终究是一个不分的“本体”。其“本”在一个创化的过程中,乃能形成天地之“体”。天地之“体”加以阴阳变化,则形成了万物之“体”,也就形成了人。人的存在也自就有“本体”,皆备于人“性”之中。而“性”又能自觉为“心”,“心”的活动便既是“理”的活动,也是“气”的活动。结合以上对宇宙创化论层面的讨论可知,“心”不但有知觉、有理性思虑能力、有主宰性,还有创化性。“心”的“本体”有其灵动性。对此,朱子认为“心”是“虚灵明觉”的。它没有滞碍,既能照明事物、反映事物的真实性,又能显示自身的活动方向与追求目标。
总而言之,朱子对“心”的讨论尚未得到细化,但他已非常全面地掌握了“心”各个方面的特质,而又尤其重视“心”的主宰性。因此,他才能继承先儒而提出“心统性情”。基于他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并不一定要以“性”来包含“心”、演化成“心”,反过来,“心”在活动之后,能发展成为“心”之体,那么,其就能以“性”为体、以“情”为用,形成了“心”“性”“情”三分的学说。这个三分之说,亦是他整合胡宏、张栻等人学说的成果。当然,胡宏、张栻依然遵循《孟子》《中庸》的传统,以“性”为“心”之所系,故“心”也只是“性”的一种表达,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体”,更不能反过来主宰“性”,而“性”本身即有主宰能力;只不过,“气质之性”更多体现为受动性,而“天命之性”更多体现为主动性。朱子固然也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这是他对二程的继承。在这个将“性”分为“天命”“气质”的层面上,“心”仍是“性”的一部分,尚不能掌握“心”的主宰活动能力。因此,“心统性情”应被视为朱子后期较为成熟的观点。不过,即便是在“心统性情”的语境下,也不能认为“性”全然为“心”所主宰、统帅,“性”当然亦有其主动的一面。这也是胡宏、张栻之说的意义所在。朱子一度同意张栻的观点,但最终觉得其有所不妥,于是能发展出“中和新说”,强调“心”的虚灵明觉和主宰统摄之能力。
“心”既能认识外在世界,又能掌握自身的“性”“情”,这正合于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8]]之义。当然,孟子并未说“万物皆备于我心”,比至陆象山,才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9]的表述,其乃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对万物与我心的思考,也类似于对“理一分殊”的思考。二程说的“性即理”,此“理”是一个广泛的、整体的“理”,而广泛整体的“理”,自然也存在一个如何呈现为具体个别事物的问题。按照朱子的理路,因为“心”中有“理”,所以人能借由“心”的知觉能力而认识个别事物。此即他在注解《大学》时所提到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明矣”。[10]不过,按他的意思,“心”要想如此有所掌握和认知,还是离不开格物致知的工夫,足见朱子并没有放弃其经验哲学式的思考要点。故我们决不能因朱子对“心”的重视而将他看成一个先天认知论者、一个内在先验知识论者。
二
在以上关于“心”之论述的基础上,我们探讨朱子的“道心”“人心”之论。“心”虚灵明觉,能认知外在世界。而“心”如何能认知善恶,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里必须要提到《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一段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1]虽然这段话出于《古文尚书》,但不减其深刻,影响也很大,深层次进入了思想史,吾人不能不面对其哲学含义。围绕这句话,朱子谈到了人心如何有善恶的这一问题。
人心之善,自然可以归于“道心”;人心若恶,不能行善,那么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人心”。这里说的“人心”,经验地看,即是人的自觉或不自觉之欲望。因为“心”具有主宰性、意向性、创化性和知觉性,所以,可以认为,“心”与外界交互影响,又会在其活动中受身体欲望或情绪影响而偏离其本身的纯净、虚灵的状态,而倒向对外在事物的追求处。朱子也承认,“人心”是受人之欲念影响的一种自然之心,必然呈现如此特质。不过,“人心”也不只有负面的意思,只是其尚未能自觉地追求善、自觉地追求代表善之行为的“道”。而人本身又完全能够合乎善,能具有善的目标、善的活动,这就被归为“道心”。所谓的“善”是什么呢?善就是人们所共同自觉肯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是有利于群体社会之繁荣充实的,是一种有利于公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妨碍他人的那种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道心”,就是能够实现善的意向和意识;“人心”则不涉及对善的实现,其兼而包含对于不太涉及善恶的一般生活欲念之追求,以及对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恶的追求。朱子对于“人心”所理应蕴含的这两方面之区别,尚未分疏得十分清楚。当然,他也提到了“口之于味”“未是不好,只是危”[12],但这种提法仍有问题。因为,在我们正常生活里的一般欲念,也无所谓“危”。相较之下,更应当这样说:“人心”具有受制于自私欲念的可能性或倾向,这种可能性或倾向才是其“危”之所在。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人又能够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规避这个“危”的问题。而且,《大禹谟》此处主要是在辨析“人心”与“道心”的区别,所称的“人心”侧重于“人心”之可能违反“道心”的角度,所以乃作此语,实是在强调人不能把人的自然之心转化成道德之心时所引致的问题。
总而言之,一般说“人心”成为恶,违反“道心”,实际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往往行而未知,并不知道其行为会如何造成实际伤害;其二,人也可能不自觉地展开私欲而忘记他人;其三,人亦可能计划性地肆意伤害他人。在这个基础上,何为“道心”也就更清楚了。“道心”就是高度自觉的自我规范,要有一种“克己复礼”的状态,要能有一种不自私的特质,避免从自我欲念出发而不考虑他人,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当然,和上面两句古典儒家的表述相比,不同于古典儒家之重视“礼”,宋明理学家更注重“理”,其实质是认为:只要合乎“理”,就不会有因私而伤害他人的举动。这就能成就“道心”。
“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与人的“性”之善恶这一命题也有关联。如上文所述,朱子曾谈到“心”之本源的问题。“心”发自于“性”,而既然“性”本就是善的、是理、是太极,那么“心”之本源就是合乎“道”的,或者说,“人心”的本源就是“道心”,其自以“道”为主;只是在成为已发之“人心”时,其就有了偏离公心、受欲念蒙蔽的可能。因此,“道心”就是“人心”的本然。如果人在活动中带有本体之“善”,那么在正常的日常活动中,“人心”就是“道心”。因此,在《朱子语类》第七十八卷里,朱子强调了“道心”对“人心”的重要作用。对于“道心”当下的位置,朱子没有给出明确的论断。但是,《大禹谟》里的“道心惟微”,实则已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心”究竟还是一直存在的,不止是在人明觉了道德规范后才有“道心”。这就又回到了朱子对“心”之主宰性的重视之处。毕竟,“惟精惟一”,即对于“心”的问题要掌握其原始点与整体性,本就合于朱子对“心统性情”的认识。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心具有“主宰性”这一命题,本就是在承认人之具备“道心”的前提下所能提出的。
人只有一个“心”,可以成为“人心”,也可以成为“道心”。故而,一定要强调从未发到已发中的审查,才能达致“道心”的实践。“人心”成为“道心”,是一种道德教化、道德转化的问题。同时,只有“允执厥中”,高度自觉,才能将行善之本加以充实,开发为用,实践为行。朱子的相关论述,可被归纳为两个方向,即“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3。“致知”一方面在于了解外在的事物,另一方面也在于启发内心的价值反思;“用敬”则在于保持原始状态,不至于失去内在的平衡与统合能力,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情况时做出相应的判断。只有在两者的内外合一之中心才能诚、正,进而合于“道”。这个诚、正之心,就是“道心”。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作者单位: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陈来
在儒家哲学中,“人”与“仁”可互为定义,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孟子所说的“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也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也是先秦儒学对“仁”的唯一定义式的表达,从秦汉到宋明,儒家学者对之做了各种解释,在现代儒学中仍然受到重视。本文就此命题及其意义进行一些讨论,以扩大分析这一问题的哲学视野。
关于“仁也者人也”这一命题,古代文献中出现了三次,并且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解释,本文则突出第三种解释的可能和意义,并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中予以强调。
一、人能亲爱施恩说
“仁也者人也”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此后又两见于《礼记》。以下我们先举出这三个材料,以供读者参考。
1.《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孟子》一书的注释,最早为汉代的赵岐,赵岐注对此的注释是: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2]仁的本义虽然可以解释为仁恩,即对他人实行恩惠,但“能行仁恩”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里的“人也”,因为不仅能行仁恩者是人,能行其他德行者也是人。
正如与这个命题的形式相同者:“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3]],其解释方法,都是要用后面的字训解前面的字,如用“宜”训解“义”,用履训解礼,用知训解智,用实训解信。按此思路,“仁者人也”应是用人来训解仁,换言之,是强调仁与人的关联,而这在赵注中却无法体现。赵注只有在孟子原文是“仁者恩也”的条件下,他的解释才能与之相合。可见赵注的注释在说明仁和人的关联上并不能令人信服。
2.《礼记》第31卷《中庸》20章: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4]
对此,《礼记正义》引述了郑玄的解释及孔颖达疏的发挥:
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疏云: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者,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〇“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宜,谓于事得宜,即是其义,故云“义者宜也”。若欲于事得宜,莫过尊贤,故云“尊贤为大”。[5]
这里是用“亲偶”解释“人也”,亲偶也就是人与人相互亲爱。仁就是去亲爱你亲爱的人。这种用亲偶解释仁、人,在先秦是没有的,也是不清楚的。可见汉儒及其影响下的解释,其实都是以仁的相亲爱的意义延伸解释的。
3.《礼记》第32卷《表记》: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礼记正义引郑注:人也,谓施以人恩也。疏云:“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爱偶也。〇“道者义也”,义,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断割得宜,然后可履蹈,故云“道者义也”。
正义:“人也,谓施以人恩也”,解经中“仁者人也”。仁,谓施以人恩,言施人以恩,正谓意相爱偶人也。云“义也,谓断以事宜也”,谓裁断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义也”。[6]
这种解释在方向上是与赵岐《孟子注》一致的,用施以人恩来解释“仁者人也”,所不同的是把仁恩与“相爱偶”结合一起,与郑玄接近。但这里对“仁者人也”的解释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无论如何,从以上已经可以看出,“仁者人也”的命题,其实并不是给“仁”下的定义,而是要强调仁与人的关联性,而如何阐明此种关联性,成为儒学史的一个课题。
二、人之所以为人说
宋代理学兴起,理学注重的是经典的思想诠释,与汉儒注重字义训诂不同。对“仁者人也”的义理解释先见于张载。《宋元学案》卷十八:
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7]
这里初步提出了“仁者人也”的“人”应解释为“所以为人”,即仁是所以为人者,这种对仁与人的关联性的说明,较汉儒为合理。
“所以为人”即是人的本质。最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完整提出了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说。朱子《孟子集注》尽心章: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8]
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然未详其是否也。[9]按照朱子的解释,“仁者人也”,其中的“仁”指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其中的“人”是指人身而言。整句是说仁作为人之理具于人之身上。其中既体现了朱子的道德意识,也体现了朱子的身体意识。
朱子《中庸章句》: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为政在人,家语作“为政在于得人”,语意尤备。人,谓贤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10]
这里提出“仁”是天地之心,也是人得以生的生理;“人”是人身,人身是具此生理的主体。
《朱子语类》中记载的朱子与学生有关孟子“仁也者人也章”的讨论有不少,这些语录进一步发挥了朱子《孟子集注》和《中庸章句》的思想: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间,浑然天理,动容周旋,造次颠沛,不可违也。一违,则私欲间乎其间,为不仁矣。虽曰二物,其实一理。盖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11]
这是说“仁者人也”是讲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说,仁是人的本质。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说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体认出来。又就人身上说,合而言之便是道也。[12]这是说仁是人之理,又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仁者人也”。人之理就是人的本质、本性。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与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犹
言“公而以人体之便是仁”也。[13总之,“仁”与“人”要互相定义,彼此不能离开,“仁”不能离开“人”去理解,“人”也不能离开“仁”去理解,必须合而言之。人是仁所依存的主体,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训仁。且如君臣之义,君臣便是人,义便是
仁;尽君臣之义即是道,所谓“合而言之”者也。[4]照朱子这个说法,“仁者人也”并不是声训之法,与“义者宜也”不同,是讲人和理义的关系,人是伦理关系的主体,理义是伦理关系的规范,仁则是理义的代表。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则不见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则人不过是一块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见得道理出来。”[15]
问:“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说仁不说人,则此道理安顿何处?只说人不说仁,则人者特一块血肉耳。必合将来说,乃是道也。”[16
这两段也是说,为什么要说仁者人也,因为讲到仁而不涉及人,则作为人之理的仁就无处寄寓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讲人而不涉及仁,人与仁、理都无关系,这样的人没有道德本性而只是血肉而已。这是朱子发挥其“理在物中”的思想来解说《孟子》的文句。
问:“先生谓外国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据?”曰:“向见尤延之说,高丽本如此。”[17]这是对《孟子集注》中“外国本”的询问,朱子的友人尤延之看到的高丽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还有对义、礼、智、信的训解,比较全面,可惜此本未传。
问:“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别物,即是这人底道理。将这仁与人合,便是道。程子谓此犹‘率性之谓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对‘义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说‘仁’字又密。止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说‘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统而言之。”淳。[18]
这是说,《中庸》的“仁者人也”,人是人身,仁是生意,强调在人身上的生生之意。这显然不是训诂的解释,而是哲学的解释。
综上来看,朱子的解释是,“仁者人也”首先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这一解释与汉儒解释不同,突出了仁与人的关系;但需要把“人”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略为曲折。其次,“人也”是强调仁具于人身,体现于人身,人身是主体。可以说朱子注孟子是哲学的诠释,不是训诂的解释,强调“仁者人也”是指仁是人的本质、人的标准。换言之,朱子认为,仁必须关联着人来定义,因为仁就是人的本质、人之理,所以孟子强调“仁者人也”。
不过,朱子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强调“人者仁也”,用仁去定义人的本质。这与“仁者人也”有所不同,因为“仁”是定名,“人之所以为人”则是不定之名,用不定之名解说仁,其意涵并没有确定。
在明代的学者中也仍有用生意发挥“仁者人也”的意旨,如《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二:
仁,生机也,己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礼则物之则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则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机?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于克己复礼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则,斯有所间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虽其一身生机,亦不贯彻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礼勿视,目得其则矣;非礼勿听,耳得其则矣;非礼勿言,口得其则矣;非礼勿动,四肢得其则矣。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则,则吾一身无往非生机之所贯彻,其有不与天地万物相流通者乎?生机与天地万物相流通,则天地万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归仁”。[19
这是说仁是生机,所谓“仁者人也”是说人的身体处处体现仁的生机,与上引朱子之说相近。很明显,宋代以后对“人也”的解释都不离开身体的意识,把身体意识与仁结合起来。
三、人指他人说
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20]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21]宋以来一般认为,这是强调仁作为人道的根本原理,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其实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即我们也可以说,“仁者人也”是指“仁”包含了他人优先的伦理原理,以下我们就来说明这一点。
《中庸》中对仁的理解,与《孟子》的“仁者人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一致,强调仁作为人道的根本原理,而仁的原理的实践,以亲亲为根本。如果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还不能简明地概括仁和义的要义,《礼记》的另一个说法“仁以爱之,义以正之”[22],则清楚地把仁和义的要义阐明了,仁的要义是慈爱,义的要义是规范。《礼记·表记》:“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这也是继续强调仁所具有的“亲而不尊”的特点,也点明了义“尊而不亲”的特点。亲亲本来是子女对父母的亲爱,孔门后学则把亲进一步扩大,如《礼记·经解》中的“上下相亲,谓之仁”,也就是发展了仁的相亲的含义,从伦理的亲爱推及于政治社会的人际关系。
仁者人也,可以说是采取一种声训的形式,即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但《孟子》《中庸》的“仁者人也”的说法,并不完全是训诂,而且还是将之作为一种表达一定哲学思想的形式。其实,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说文解字》的解释“仁,亲也”是和郑玄的《礼记注》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不能解释“人也”二字。宋儒把“人也”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也还是曲折了,不太可能是先秦儒的本义。现代训诂学也接受了宋儒的说法,其实,并不一定要采取这种过分哲学化的诠释。
若分析起来,有一个简易的训诂意义被宋以来的儒学忽略了,即“人也”的“人”是“人我”之人,即指“他人”。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汉代儒学的仁学如果说有何贡献的话,应该说主要表达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在《礼记·乐记篇》中曾提出“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但并没有说明爱和正的对象。而《春秋繁露》最集中表达的是,“仁者爱人、义者正我”,在仁义的不同对象的对比中阐释他们各自的意义。董仲舒提出: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23]
与《荀子·子道篇》“仁者自爱”说不同,董仲舒明确主张,“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认为一切道德无非是对他人或对自我而言的,“仁者人也”的意思,就是着眼于他人,仁是仁爱他人的德行;相对于仁者人也,则是“义者我也”,表示义是纠正自己的德行。仁作为“爱”是爱他人,不是爱自己;义作为“正”是正自我,不是正他人。这个对比的说法是先秦儒学其他各派中所没有的。他认为,自爱而不爱人,这不是仁。仁的实践必须是他者取向的,义的实践则必须是自我取向的。可见,董仲舒对仁义的讨论,重点不是价值上的定义,而是实践的对象,是密切联系着仁的实践的。董仲舒对“仁”与“人”的关联诠释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伦理意义,此即他者的人道主义,这一点以前都被忽略了。近人梁启超也说:“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常在我也。”[24]也是把“仁者人也”的人理解为人我之人。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解释,儒家的伦理是尊重对方的为他之学,而非为己,为他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在梁漱溟表述的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伦理正是列维纳斯所谓的“他者的人道主义”而不是“自我的人道主义”。
在某一个方面来看,仁正是如此。在伦理上,仁不是自我中心的。宋明儒学喜欢讲儒学就是为己之学,这仅就儒学强调个人修身的方面来说是不错的,儒家讲“克己”,讲“古之学者为己”,都是这方面的表现。但是儒学并不能完全归结为为己之学。仁的伦理意义和修身意义是不同的,伦理的仁指向他人,修身的仁指向自我,这是要分别清楚的。孔子仁学中总是有两方面,克己和爱人是这样,修己和治人也是这样。“内圣外王”的说法虽然最早出于《庄子》书中,宋明理学家也不常用这个概念,但孔子讲的修己治人与内圣外王相通。故孔子以来儒学本来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而仁学不仅是克己,更是爱人,不仅是为己,也是为他,这在汉儒对仁的伦理界定看得最为清楚,也是汉儒的贡献。所以,直到唐代的韩愈仍然以汉儒为出发点,以博爱论仁,博爱指向的正是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我们的诠释,孟子所说“仁者人也”中的“人”字亦即是“他人”之意,是人己之人,是人我之人。董仲舒是最先肯定这一点的儒学家,“仁之为言人也”这一思想虽然并不是在对《孟子》或《中庸》“仁者人也”的注解或诠释中提出来的,但实可以作为“仁者人也”的一种理解和解释。在事实的层面,我们看到很多能克己的人却不一定能尊重他者、亲爱他者。因此,做人与为仁,既要克己修身,又要爱人亲民;做人与求仁不仅要去除私欲,严谨修身,还要克服自我中心,以他者为优先;做人与践仁不仅体现在对控制欲望的自我修养上,也体现在如何对待他者、他性,如何体现恕道,这是以往较受忽视的地方。今天我们重提“做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仁者人也”这一问题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一个文本根据不同理解可有不同意义,文本的意义可以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视界融合而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对“仁者人也”的三种理解而言,无须以其中一种去彻底否定其余两种,而应该承认这些理解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思维,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人们对儒学仁论或人论的理解。
四、仁者人也的现代诠释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怎样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呢?
1.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法意味着这些价值的适用性不仅在一个国家之内,更适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和关系。简言之,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更是指适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应是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故也可称为“世界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提出,是把原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价值“世界化”,以构建合理的世界秩序。
关于基本价值的世界化、国际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自由、公平是20世纪西方世界特别重视的价值。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奉行民主、自由、公平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他们并不是“普适”的,只是其国内的政治价值,不是世界的价值。在世界事务中他们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公平即主张各个国家一律平等,民主即世界大事要共同商量,反对大、强、富国欺压小、弱、贫的国家。人类共同价值是要把这些价值真正扩展到人类所有事务,使之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价值。
2.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伦理”运动。世界伦理又称全球伦理,在我看来二者略有区别,世界伦理可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的行为准则,而全球伦理则指跨文明的人类行为准则。这就引出一个讨论,“世界伦理”是不是“人类共同价值”?从被一致公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看,应该说世界伦理即是一种价值观,也是谋求确定人类基本的价值共识,全球伦理就是要展示人类基本价值和道德。因此,“世界伦理”应当属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伦理基础。区别在于,世界伦理的指向,是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然不限于个人),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以国家为单位,指向国际关系,并不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别对应三个层次,即个人、社会、国家,而“人类共同价值”则针对在“国家”之上,是第四个层次,是国家之间的世界。这就使我们对价值的认识形成四个层次,世界、国家、社会、个人,更为完整。
然而,真正确立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之间的世界政治层面。我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必有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世界伦理。没有世界伦理,特别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共同价值就不完全,就缺乏道德的基础,也就不能找到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关系角度。
3.有了伦理道德基础的角度和视野,我们就能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关系。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应该说表达了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总体而言,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分而言之: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是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第四,“以德服人”,王道正直,是“和平”的基础;第五,“天下为公”,不以私利为原则,是“正义”的基础(如全球气候问题及其义务分配)。
这五项不仅可以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成为这些价值后面的深层理念,它们本身也是人类生活最基础的道德价值。故人类共同价值除了世界事务、国家间关系的价值约束外,也同时是人类一切生活所必需。由此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原理的普遍意义。
其实,上述五点都是儒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这也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仁”与“人”的关系,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对“仁者人也”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诠释,即“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或“仁是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原理”。
(论文前三部分载于《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朱熹论“人心”与“道心”
——从心的主体化与主宰性到道德心的实践
﹝美〕成中英
一
朱子曾讨论“人心”与“道心”的差别,并涉及了“人心”如何能实现“道心”这一命题。通过围绕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可以凸显朱子心性之学的特点与得失。首先有必要回溯朱子对“心”的认识以展开讨论。朱子对“心”的认识,有其包含性与深刻性。他既整合了两宋理学家对“心”的认识,又重新系统而深刻地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所涉及的“心”之概念的含义。
1971年,笔者曾撰文论述中国古典儒学中“心”的概念,指出:《中庸》着重探讨了“性”的问题,多次举“性”字发论,辨析“性”的功用,但罕有对“心”的说明,至少没有明显地论述“心”;《大学》探讨了“心”,但对“性”的论述则较少。在《孟子》处,既谈了“心”,也谈了“性”,且此二者在孟子看来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有道德感情,发而为四端,四端皆可谓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这里的四端之“心”,均直接指向一种“心”的活动,其又能用来说明人的“性”之为善。因此,在早期儒家学说中有这样一种古典的论述:“心”是“性”的表达。[1]
到了宋代,胡宏对这种古典的论述有了新的表达,认为“性”是体,“心”是用。不过,朱子对此又有别样的认识。朱子的看法,既结合了张载、二程的学术传统,又体现了人的直觉经验,故而有了新的认识。他的看法至少应该被认为包含了以下两点:(一)“心”就是知觉,人所谓有“心”,也就是有知觉能力,张载和二程也均做了类似的肯定(而佛学中的“五蕴”也是在说明“心”的知觉或感觉之能力);(二)“心”是一种主宰,它“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2],此说大抵在他近40岁时与张栻论学后才整合得出,是他处理“心统性情”之提法的重要认识前提。对于“心”作为主宰这一思想的根源,吾人可以追溯至荀子处。在《解蔽篇》中荀子明白地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3]这里强调了“心”自主活动的能力,即属于彰显“心”之主宰性的说法。所谓“心”能作为主宰,一方面表明其有自我控制、自我确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指它能影响与其有关的性情,即朱子所发扬的张载的“心统性情”说。
至此,吾人应该分析“心”与“性”的关系。首先,“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特质与潜能。古典儒家很早就重视“性”这一概念,孔子即强调“性相近,习相远”[4]],又说“人之生也直”,这里的“生”与“性”是相互联系的,“生”的表现就是“性”的表现。孔子以“直”训“生”,一方面能表“直接”义,也就是说,兹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表现,其并非是在曲折地表达某些不可知的东西,而是在直接地显明其特质;另一方面,“直”又可能带有道德含义,也可被训为“正直”。事实上,“直”是“德(悳)”字的一部分,本身可能就具有好、善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本是趋向于善的,并以趋向于善为善。从宇宙论的角度看,人之生命的出现,更可以被视为是“善”的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生”就是“善”的,生生不已的发挥、发展也是“善”的,“善”亦自与“生”相关联。因此,《易传》乃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5]]。能继承生命的本源,并将其发挥下来,持续地发展其内在的能力、表达其内具的德性,这就是“性”,而从其根源上讲,这又是“善”。这就是古典儒家从孔子到《易传》对“性”所具有的深刻体验。
而“性”也可以被表达出来。当其未发之时,还处在一种内在的状态。“性”的内在性和它的外在性(表达性),存在着一种从未发到已发的对立。以《中庸》言之,若其已发,则即发为“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犹然是和自然“性”相关的,那么,自然“性”如何与道德“性”建立关联、形成转化,就尚需要深刻的分析与探讨了。对此,朱熹将“性”的表现称之为“情”,同时,在注解《孟子》时,他又将“恻隐之心”的“心”训为“情”。他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6]广义的“心”应该包括知觉力与主宰性,但对于《中庸》所说的“未发”而言,这种“未发”究竟是“性”之未发还是“心”之未发,仍是值得讨论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即便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心”与“性”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难以割裂。以我观之,“心”是“性”的一种流露,而这种流露又以“情”的方式得以外在表现。“喜怒哀乐”既然能“发”,当然是“情”;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朱子认为也是“情”。这种“情”,是道德之“性”的基础,故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作为“情”的四端之心,表达的是一种“性”的真实不虚,是一种道德、价值与伦理。而这种“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必须被实现出来,且必须随时能被实现出来。当然,具体如何才能把“性”之本然具有的内在之德,实现为表达此道德之“性”的“情”,其中的理路在朱子与其他古代儒者那里,其实是有扦格与跳跃的。
除了“情”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考虑“意”这一范畴。之所以要在“情”外更讲“意”,是因为存在一类意向性的问题。“情”如果不能展现为“意”,就不能成为行为的基础。因此,“情”尚不是最向外的一环,其更为外发则应归为“意”。所谓“意”,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导向与动力。
那么,在将“意”也考虑在内后,“心”究竟是什么呢?朱子在注“四书”时,实际上已经对“心统性情”这一说法有了深刻的了解。这和他的“中和新说”有密切关系。他扭转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传统中可以说,“性”是从“心”里开展出“情”,继而可再说从“情”里开展出“意”。朱子则以“心统性情”的方式调和了几个范畴间的关系。“心”除了有知觉力与主宰性外,还有一种理性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单纯的知觉力相区别的。“心统性情”这一命题,在彰显“心”的理性认知、价值判断方面,尚有未尽,但在高扬“心”的统帅能力处,则非常透彻,足以体现朱子对“心”有着认识深刻的一面。不过,这样也改变了某种对“心”“性”之间内在结构的认识。
依照古典儒学的观点,“性”后有“心”,没有此“性”就没有此“心”,比如,“恻隐”之心等四端,均是基于“性”而能发的。在这个意义上,“性”才是本,而“心”是可被摄入“性”之中并逐渐自然觉醒开发出来的。这确是人的特点。很多动物并不可谓有“心”的概念,它们只有本能,只有动物性,而决不可谓有“心”。究其原因,在于动物虽有知觉,但无主宰。它们都可以被条件化,故不能说有主宰。对于外部的世界,它们更不可能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只是基于本能而为满足欲望做出觅食等事罢了。因此,也不可说动物有一种“理”的自觉,仅是处在“气”的运行之中而已,这也是判定其不可言“心”的理由之一。所以,“心”似乎确应作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
朱子的观点则与此不同。通过整合先秦儒者与二程的观点,他实际上有着如下这样的理路。“心”在从“性”中发展出来后,自觉为“心”,本是“性”的一部分,比如《性自命出》里就提到了人虽有性但心无定志的问题,孔子也说“从心所欲”,在这个意义上,心是有其来去无定之自由活动性的。“从心所欲”之所以能“不逾矩”,是因为其“性”在匡正着“心”,于此,“性”规定了“心”的活动范围,在“心”与“性”直接,“性”仍是主动的。在这里,透过一定的自觉修持,“性”具有一种潜力,可以约束随时发生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实则是一种以“心”为主体的欲望。这种欲望可以是身体的欲望,但其毕竟又透过“心”的方式得到自觉的表达。换言之,一旦有了自觉的意识,就有了“心”的存在。这就使“心”作为主体而存在,将“性”的主体性转化成了“心”的主宰性。
作为一个主体,“心”固然是源于“性”的,但若以我所常用的“本体”概念观之,则能清楚地厘清两者的关系。“性”是一个“体”,可谓之性体。此性体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内里涵有一些表达与行为的活动能力。而这种能力有一定的方式、方向,具备目的性。具有这样内涵的“性”,引起了一种自觉,即成为“心”,产生了一种“心”的主体性。所谓“心”的自觉,即是“心”能自己了解其自身,觉知其之所以存在为其自身,形成了自己的“体”。
“性”之本即是“理”,这个“理”,是天地之理。不过,“性”也是通过气质的存在来得以实现的,需要气质作为其载体。所以,宋明理学宇宙论的基础,即在于对“理”与“气”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是对外在之宇宙世界的观察,也建筑在人之存在的内在观察上。从外在观察即宇宙观察的角度看,人之为人,能看到天地之变化,能看到天地运行的规则,即《易传》所提到的观天察地之事。《易》认为人能在观察中掌握宇宙变化之道,乃据此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7],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易学哲学。因此,人的存在既有“气”的成分,也有“理”的成分。当二程说“性即理”的时候,就是指“性”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有着内在的价值。“性”同样也兼具“气”的成分与“理”的成分。就宇宙本体论而言,朱子也探讨了“性”与“理”的关系。朱子将两者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二元的关系,认为两者间是相互作用的。不过,从《朱子语类》第1卷中的表述看,他又认为“理”究竟是最终的存在。这与之前他理气相须的说法间即尚有需要调和之处。
既然朱子认为太极在其作为终极存在的意义上就是“理”,那么,“理”作为一个可等同于太极、涉及存在之本的范畴,就必然及于“气”。在这个意义上,创化之“理”又是“道”。这样一来,朱子认为太极只是“理”,便终究有自相矛盾之处,因其必然也是“气”。理气于此是合一的。只不过“理”“气”可分而被视为形式与质料、动力与目标罢了,但其终究是相互依存、不能分开的,终究是一个不分的“本体”。其“本”在一个创化的过程中,乃能形成天地之“体”。天地之“体”加以阴阳变化,则形成了万物之“体”,也就形成了人。人的存在也自就有“本体”,皆备于人“性”之中。而“性”又能自觉为“心”,“心”的活动便既是“理”的活动,也是“气”的活动。结合以上对宇宙创化论层面的讨论可知,“心”不但有知觉、有理性思虑能力、有主宰性,还有创化性。“心”的“本体”有其灵动性。对此,朱子认为“心”是“虚灵明觉”的。它没有滞碍,既能照明事物、反映事物的真实性,又能显示自身的活动方向与追求目标。
总而言之,朱子对“心”的讨论尚未得到细化,但他已非常全面地掌握了“心”各个方面的特质,而又尤其重视“心”的主宰性。因此,他才能继承先儒而提出“心统性情”。基于他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并不一定要以“性”来包含“心”、演化成“心”,反过来,“心”在活动之后,能发展成为“心”之体,那么,其就能以“性”为体、以“情”为用,形成了“心”“性”“情”三分的学说。这个三分之说,亦是他整合胡宏、张栻等人学说的成果。当然,胡宏、张栻依然遵循《孟子》《中庸》的传统,以“性”为“心”之所系,故“心”也只是“性”的一种表达,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体”,更不能反过来主宰“性”,而“性”本身即有主宰能力;只不过,“气质之性”更多体现为受动性,而“天命之性”更多体现为主动性。朱子固然也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这是他对二程的继承。在这个将“性”分为“天命”“气质”的层面上,“心”仍是“性”的一部分,尚不能掌握“心”的主宰活动能力。因此,“心统性情”应被视为朱子后期较为成熟的观点。不过,即便是在“心统性情”的语境下,也不能认为“性”全然为“心”所主宰、统帅,“性”当然亦有其主动的一面。这也是胡宏、张栻之说的意义所在。朱子一度同意张栻的观点,但最终觉得其有所不妥,于是能发展出“中和新说”,强调“心”的虚灵明觉和主宰统摄之能力。
“心”既能认识外在世界,又能掌握自身的“性”“情”,这正合于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8]]之义。当然,孟子并未说“万物皆备于我心”,比至陆象山,才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9]的表述,其乃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对万物与我心的思考,也类似于对“理一分殊”的思考。二程说的“性即理”,此“理”是一个广泛的、整体的“理”,而广泛整体的“理”,自然也存在一个如何呈现为具体个别事物的问题。按照朱子的理路,因为“心”中有“理”,所以人能借由“心”的知觉能力而认识个别事物。此即他在注解《大学》时所提到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明矣”。[10]不过,按他的意思,“心”要想如此有所掌握和认知,还是离不开格物致知的工夫,足见朱子并没有放弃其经验哲学式的思考要点。故我们决不能因朱子对“心”的重视而将他看成一个先天认知论者、一个内在先验知识论者。
二
在以上关于“心”之论述的基础上,我们探讨朱子的“道心”“人心”之论。“心”虚灵明觉,能认知外在世界。而“心”如何能认知善恶,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里必须要提到《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一段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1]虽然这段话出于《古文尚书》,但不减其深刻,影响也很大,深层次进入了思想史,吾人不能不面对其哲学含义。围绕这句话,朱子谈到了人心如何有善恶的这一问题。
人心之善,自然可以归于“道心”;人心若恶,不能行善,那么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人心”。这里说的“人心”,经验地看,即是人的自觉或不自觉之欲望。因为“心”具有主宰性、意向性、创化性和知觉性,所以,可以认为,“心”与外界交互影响,又会在其活动中受身体欲望或情绪影响而偏离其本身的纯净、虚灵的状态,而倒向对外在事物的追求处。朱子也承认,“人心”是受人之欲念影响的一种自然之心,必然呈现如此特质。不过,“人心”也不只有负面的意思,只是其尚未能自觉地追求善、自觉地追求代表善之行为的“道”。而人本身又完全能够合乎善,能具有善的目标、善的活动,这就被归为“道心”。所谓的“善”是什么呢?善就是人们所共同自觉肯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是有利于群体社会之繁荣充实的,是一种有利于公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妨碍他人的那种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道心”,就是能够实现善的意向和意识;“人心”则不涉及对善的实现,其兼而包含对于不太涉及善恶的一般生活欲念之追求,以及对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恶的追求。朱子对于“人心”所理应蕴含的这两方面之区别,尚未分疏得十分清楚。当然,他也提到了“口之于味”“未是不好,只是危”[12],但这种提法仍有问题。因为,在我们正常生活里的一般欲念,也无所谓“危”。相较之下,更应当这样说:“人心”具有受制于自私欲念的可能性或倾向,这种可能性或倾向才是其“危”之所在。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人又能够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规避这个“危”的问题。而且,《大禹谟》此处主要是在辨析“人心”与“道心”的区别,所称的“人心”侧重于“人心”之可能违反“道心”的角度,所以乃作此语,实是在强调人不能把人的自然之心转化成道德之心时所引致的问题。
总而言之,一般说“人心”成为恶,违反“道心”,实际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往往行而未知,并不知道其行为会如何造成实际伤害;其二,人也可能不自觉地展开私欲而忘记他人;其三,人亦可能计划性地肆意伤害他人。在这个基础上,何为“道心”也就更清楚了。“道心”就是高度自觉的自我规范,要有一种“克己复礼”的状态,要能有一种不自私的特质,避免从自我欲念出发而不考虑他人,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当然,和上面两句古典儒家的表述相比,不同于古典儒家之重视“礼”,宋明理学家更注重“理”,其实质是认为:只要合乎“理”,就不会有因私而伤害他人的举动。这就能成就“道心”。
“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与人的“性”之善恶这一命题也有关联。如上文所述,朱子曾谈到“心”之本源的问题。“心”发自于“性”,而既然“性”本就是善的、是理、是太极,那么“心”之本源就是合乎“道”的,或者说,“人心”的本源就是“道心”,其自以“道”为主;只是在成为已发之“人心”时,其就有了偏离公心、受欲念蒙蔽的可能。因此,“道心”就是“人心”的本然。如果人在活动中带有本体之“善”,那么在正常的日常活动中,“人心”就是“道心”。因此,在《朱子语类》第七十八卷里,朱子强调了“道心”对“人心”的重要作用。对于“道心”当下的位置,朱子没有给出明确的论断。但是,《大禹谟》里的“道心惟微”,实则已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心”究竟还是一直存在的,不止是在人明觉了道德规范后才有“道心”。这就又回到了朱子对“心”之主宰性的重视之处。毕竟,“惟精惟一”,即对于“心”的问题要掌握其原始点与整体性,本就合于朱子对“心统性情”的认识。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心具有“主宰性”这一命题,本就是在承认人之具备“道心”的前提下所能提出的。
人只有一个“心”,可以成为“人心”,也可以成为“道心”。故而,一定要强调从未发到已发中的审查,才能达致“道心”的实践。“人心”成为“道心”,是一种道德教化、道德转化的问题。同时,只有“允执厥中”,高度自觉,才能将行善之本加以充实,开发为用,实践为行。朱子的相关论述,可被归纳为两个方向,即“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3。“致知”一方面在于了解外在的事物,另一方面也在于启发内心的价值反思;“用敬”则在于保持原始状态,不至于失去内在的平衡与统合能力,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情况时做出相应的判断。只有在两者的内外合一之中心才能诚、正,进而合于“道”。这个诚、正之心,就是“道心”。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作者单位: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附注
注释:
[1] 陈荣捷的英译如下:Mencius said,“Humanity is(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man.When embodied in man's conduct,it is the Way.”See Wing-tsit Chan,ASource Bookin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81.
[2]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77页。
[3]见《朱子语类》卷六一,朱子因尤延之语而述高丽本孟子语:“尝闻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丽本云: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说近是。”
[4]陈荣捷先生对“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的英译为: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 is to be done through the Way,and the cultivation ofthe Way is to be done of humanity.Humanity is(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of)man,and the greatest application of it in being affectionate toward relatives(parents).See Wing-tsit Chan,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3,pp.104.
[5]孔颖达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12~2014页。
[6]同上注,第2058~2060页。
[7]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4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7页。
[9]同上。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1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9页。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9~1460页。
[17]同上注,第1460页。
[18]同上。
[19]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08~609页。
[20]《孟子·离娄上》。
[21]《孟子·尽心下》。
[22]《礼记·乐记》。
[2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43~245页。
[24]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第35页。
参考文献:
[1]CHUNG-YING CHENG,“Some Aspects of the Confucian Notion of Mind”。《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71年第20期。
[2]朱熹,《朱子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2页。
[3]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98页。
[4]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4页。
[5]孔颖达,《周易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7]孔颖达,《周易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
[8]焦循,《孟子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49页。
[9]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
[10]孔颖达,《周易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11]同上。
[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3页。
[13]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88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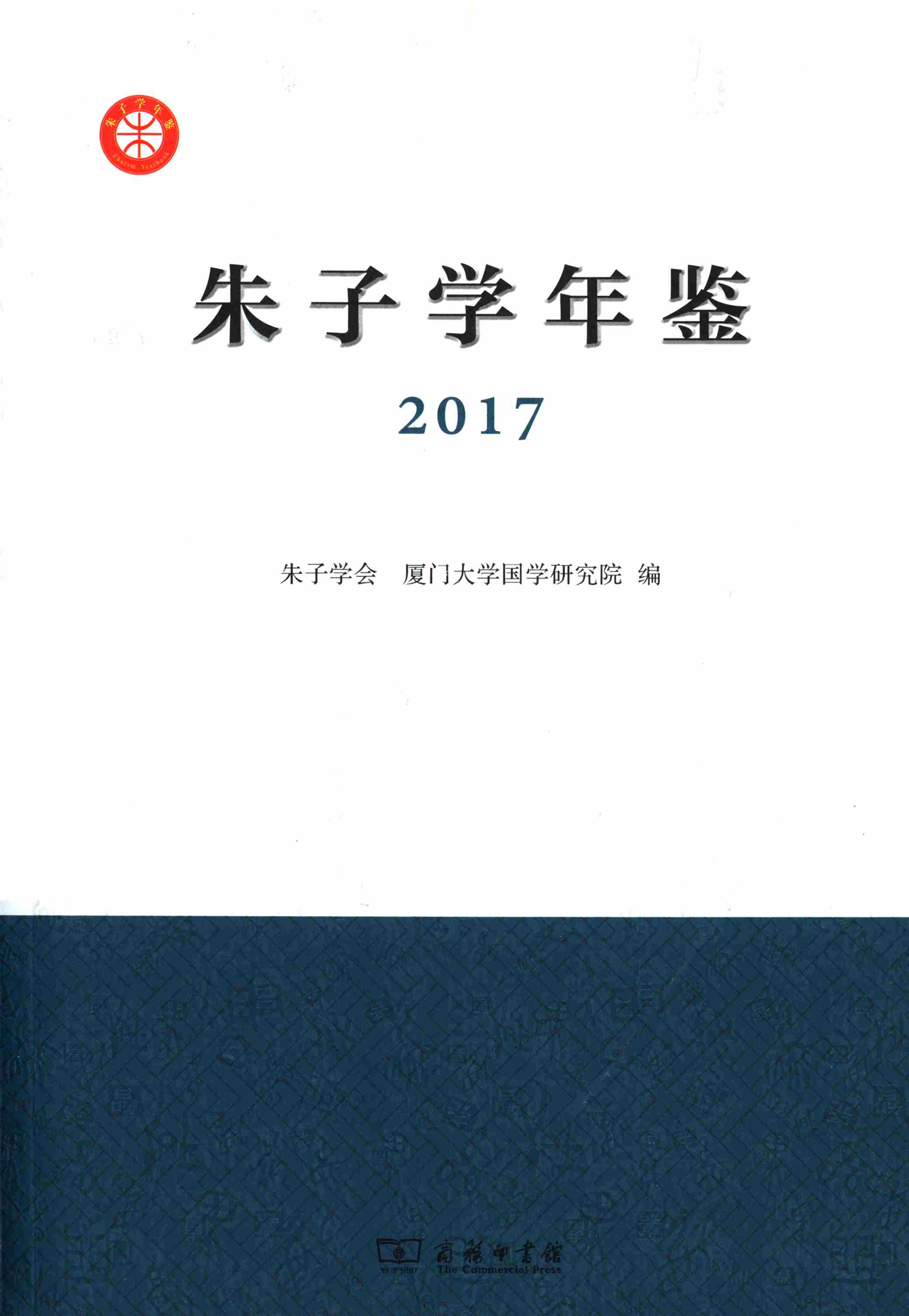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7》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仁者人也”新解》《朱子学的构建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朱熹与陈亮往来书信编年考证》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