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4》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707 |
| 颗粒名称: | 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3 |
| 页码: | 129-191 |
| 摘要: | 本文收录了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的文章,其中包括了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研究成果提要、2014年香港朱子学研究综述、2013—2014年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等。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研究述评 |
内容
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研究成果提要
郭雨颖
综观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有关朱子学研究及其出版的情形,朱熹(1130—1200)思想体系以及朱子学等相关研究仍然十分丰赡,这些研究或从经学、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的领域、视角来探讨朱子本身的关怀,甚或是研究朱子学的发展。此外,还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台湾学界在近十多年来有关朱子学研究的课题,亦开展出新的视野,这种研究视野主要是以“东亚”作为一个考察儒学的视角,尤其又聚焦在对“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的关注上,由此更为深化,并且更加充实了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因此,以“东亚”的脉络来重新检视儒学,乃至于朱子学论题的研讨会、演讲,甚至于课程的讲授等,亦多有所见。
据初步调查,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对朱子思想或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的统计,专书计有3本,期刊论文有44篇,专书论文有6篇,学位(硕、博士)论文共有15篇,会议论文47篇,更有十余次的专题演讲主题以朱子思想及朱子学者作为关键词。(详细资料请参考“2014年台湾地区朱子学研究相关资料”)以下就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
一、学术会议及演讲
先就学术会议做一简述。本年度举办以儒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共计有四场,其中即有一场是专门以朱子学为研究课题的国际研讨会,依举办的时间顺序,胪列于下:
(1)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台湾朱子研究协会、台湾中文学会、中华朱子学会主办,“朱子哲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14年3月14—15日。[1]
(2)台湾师范大学东亚文化与汉学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跨文化视域下的儒家伦常:政道与治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2014年9月26—27日。
(3)“中央大学”中文系、“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宋明清儒学的类型与流变”学术研讨会,桃园:“中央大学”文学院,2014年10月30—31日。
(4)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儒家思想与儒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南:成功大学文学院,2014年11月21日。
在上述的会议当中,即多可见针对朱子学、“四书”学等相关领域,乃至于海外朱子学等主题的论文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亦于同年出版,刊载于各大学术期刊。
其次,诸多针对朱子学的演讲亦采取新的视角来加以阐说,如关西大学的吾妻重二教授即以《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为题来提出他的观察,吾妻氏认为朱子学所揭示的重点在“格物致知”,即所谓重视“理智”,是一个爱“知”的综合性学问体系。然就现今学术研究而言,对朱子学这一综合性学问体系则多聚焦在形上层面的哲学、思想领域,但吾妻氏认为这样并不足以撑开这一名为综合性的学问体系,他说:
迄今为止,朱子学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领域,也就是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哲学侧面的分析。当然,朱熹的学问具备了在他之前中国思想所没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因此无疑应该重视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充分理解朱子学,也是事实。[2]吾妻氏认为,朱子学作为中国近世以降的思想母胎,其思想史地位固然重要,只是,这当中尚有许多可供开发的论题,就中国脉络而言,可关注朱子的教育论及其实践;而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多可着眼在朱子学当中的礼学与礼制的研究上,如《朱子家礼》对于“冠昏丧祭”四礼的规定等。
同时,吾妻氏亦提醒我们,应当注意朱子主张“理一分殊”当中“理”的普遍性,而且他把“理”比作朱子学自中国远播至东亚世界后所形成的普遍性之“理”,换言之,即关注朱子学在域外的发展。朱子学之“理”于东亚世界形成的普遍性,这种观察并非吾妻氏孤明先发。事实上,早在日本德川时代,由僧入儒的藤原惺窝(1561—1619)在其《惺窝问答》《舟中规约》等文章,甚至于替幕府起草的官方外交文书《致书安南国》中,再三申阐朱子思想体系,以由“理”作为命题所组构而成的普遍主义,借以强调此“理”、此“性”系人与生俱来即有,并不为各国不同的文化风土所囿限。是以,吾妻氏认为能自惺窝的认识当中窥见,朱子学在当时东亚世界中被广泛接受,具体的表现在于书院的教育、礼制的规定等两大层面,其中,《朱子家礼》更是成为东亚世界所广泛采纳的礼仪准则,即使时至今日,仍可将这套礼节视为“活”的传统。[3]
如上所述,吾妻重二教授揭示了《朱子家礼》对于中国,甚至东亚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性,相较于此,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则是以《朱子家训》作为分析文本。朱氏首先将《家训》与中国历代著名的家训做一比较,他认为,《家训》并不如同其他家训洋洋洒洒,动辄载录数万言的长篇巨制,反而是颠覆旧有的典型,其关键乃在于《家训》全书仅317字之多,便于记诵、利于传播,据此,朱氏指认《家训》呈现出它的“普世”性。[4]再者,《家训》本来虽只是在朱氏家族内部流传,但它以通俗、精练的文字来加以缮写,更是具体指出作为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约束,从而打破既有的界域,证明了其“普世化”的意义。
二、专书
关于2014年度朱子学相关研究的专书,若算上翻译本,则可指出以下三本,分别是:李蕙如的《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胡春依的《朱熹、袁甫与黎立武的四书诠释及其比较》,以及由日本学者佐野公治著,庄兵、张文朝翻译,并由林庆彰进行校订的《四书学史的研究》。限于篇幅,以下仅就李蕙如一书略做介绍。
李蕙如《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一书,系由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改写出版,全书共分六章,以及附录一篇,章节架构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第三节 研究之方法与步骤
第二章 许衡其人及其书
第一节 许衡生平传略
第二节 许衡著作介绍
第三章 许衡对先秦儒道思想之评论
第一节 对孔孟思想的评论
第二节 对先秦道家思想的评论
第四章 许衡推动朱学官学化的历程
第一节 发轫期
第二节 发展期
第三节 完成期
第五章 许衡的影响及历史评价
第一节 许衡的影响
第二节 历代对许衡的评价
第六章 结论
参考书目
附录
以全书的章节安排来说,作者将重点安排在第四章,即关注在宋元鼎革之际许衡(1209—1281)是如何在异族的统治下,致力于程朱理学之推动,后使其官学化的过程。作者指出,理学官学化运动,在早先的南宋时期即已产生,如真德秀(1178—1235)以及魏了翁(1178—1237)曾倡尊理学,但是,终宋之世,理学的官学化终究没有达成,即使理学在理宗朝时得到官方的认可,却始终未能将其制度化。作者认为,这种理学官学化运动,主要系出于许衡的擘画。[5]
作者指出,许衡作为一个汉人儒者,他试图在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体制下,通过与政治力量合作的方式,使国家步入正轨,而这首要工作便在于“恢复儒治”,即“行汉法”,如采取通过经筵讲学、以儒道治国,乃至推动教育、使国子监书院化等具体行为。此外,许衡更致力于朱子学的通俗化,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易简”的学术诉求上,如他在解释“道”字时说:“众人之所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其认为“道”应该是一贴近众人之事,举凡日常生活所需之盐米物资、人伦日用之事,皆是属于广义而言的“道”之范畴。[6]
许衡对朱子学的继承,较具有思想体系的脉络,这主要可从他的“四书”学上探知。作者指出,许衡论《大学》时,特重“修身”,故有“大学之教最紧要全在修身上”之语,又尤当许衡将此“修身”工夫明确地归于皇帝之时,借以强调君王本有的“絜矩之道”,据此,作者认为许衡之所以重视“修身”之教的原因,其关键在于“修身即是正心,身正即是心正,因此,一心正则家正、国正,心正是天下的体例”,许衡认为正心是“修身”的“根脚”,同时也是治国之根本。关于“修身”所应因循的路径,许衡则遵循朱子所言,认为应系于“敬”一字,但许衡认为此“敬”并非单纯讲求内在修养,而是必须内外兼具,是以他将其分疏为二:其一为“心术正乎内”,其二则为“威严正乎外”。[7]
论及朱子学最核心的命题“格物致知”时,许衡则有其不同的见解。作者指出,许衡认为“正心”之前尚有“格物”“致知”“诚意”等工夫,但此三者皆必须在“心”上下功夫,据此,如许衡在解释“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以及“致知在格物”两句之时,皆重视“心”的意义及其作用,用作者的话来说,即“主张致吾心之知,穷吾心之理,把格物致知和尽心知性联系起来”。[8]如此,在“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的先后问题上,许衡即一反朱子之道,其所主张则是“分知行为二事、提倡真知力行,主张知行并进、先务躬行”,这同时也构成许衡学说当中的重要命题。[9]
提到《论语》与《孟子》之时,作者指出,许衡主要把儒家的天道观念放在政治问题中进行讨论,故而当许衡论及天命,尤其是着眼于“命”的观念时,自然不会是术法家所言的宿命,更不会是释、道思想下的范畴,他所指摘的是“不可变易的自然秩序”,这一点,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于封建社会的认识上,他将封建社会视为自然秩序。[10]至于许衡对《中庸》的理解,他师法程朱,将《中庸》之道视为“着实有用”之学问,并以此来批判佛老的虚无之教。此外,许衡虽同样接受程朱有关“理”的说法,但他更重视的是将“理”的作用与价值落实到具体的事物上,而非仅是作为万物的发生源。换言之,即许衡重视的是“物”与“理”两者之间的“不可相离”。[11]
许衡对于朱子学的绍述、传衍,理解与批判,均可视为是他推行朱学的发展期。然而,元代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完成,主要落在元廷将朱注“四书”正式颁订为科举制度下的考试定本,是年为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意即,终许衡一生对于程朱理学的推行,但到其辞世之前,科举制度皆未能施行,不过,许衡在推动程朱理学官学化过程中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在科举制度颁行的同年,许衡也得以配祀于孔庙,官方更成立书院以提倡许衡之学。[12]职是之故,就以元代官方对于许衡功业如此重视的情形来看,可见他对朱学传承以及朱学官学化的贡献,在政治、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具其重要性。
三、期刊论文、专书论文
在2014年度的学术期刊中,有将朱子学相关议题的探讨订为专号,篇中亦收录有关朱子思想的精彩论著,如《哲学与文化》在第41卷第5期中制作了“朱王对比专题”,其后,在第41卷第8期中又制作了“韩国儒学的人物性同异论之研究专题”,此两期专辑所收录之论文,主要涉及朱子学的比较、诠释与再现(韩国朱子学)等课题,同时亦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新视野。
此外,在专书论文的部分,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在其新书《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中,收录了《儒家历史叙述的特质:朱子历史叙述中的圣王典范》以及《儒家历史解释的理论基础: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两篇修订后的旧文。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则是在其主编的《自然概念史论》当中收录《理学论述的“自然”概念》一文。另一方面,金永植教授探讨朱子自然哲学的相关研究亦被翻译成中文,如有《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与《朱熹“格物”与“致知”方法论中的“类推”》两文,被收录在他最新出版的《科学与东亚儒家传统》一书当中。[13]
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有关朱熹思想以及朱子学的研究论文,殆可粗分为五类,以下,依各论文论旨做一略述:
(一)朱熹思想与观念问题
本年度关于朱熹思想与观念问题的研究论著,可以举出许朝阳《挂搭与相衮:朱子的理气型态及其对“恶”的处理》、王雪卿《朱子工夫论中的静坐》,以及冯兵《情感性·宗教性·实践性——朱子礼学观的三重维度》三篇文章。
就中国台湾学界对宋明理学的解析与分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属当代新儒家牟宗三(1909—1995)。牟宗三主要将理学归类为两种型态:其一为“即存有即活动”,二则为“即存有不活动”,据此分系,朱子的思想系属后者。许朝阳一文即尝试在此框架下提出不同的看法。在通过与印度数论派哲学中的“神我”(purusa)与“自性”(praksti)对比之下,作者指出,朱子之理呈现两种不同的型态,首先,朱子在论现象的发生时使用“理挂搭在气上”之句,以“挂搭”来指认理气关系的确符合理不活动的推论,此系理的“消极参与”。但是,在朱子的认识里,理亦内寓于事物当中,即所谓“天地万物莫不有理”,故可推知善之事物,有其善之共相,恶之事物亦然,据此,作者指出朱子理气论下的“相衮”型态,此则理之“积极参与”,是为第二种型态。因此,朱子之学并非如数论派哲学所申阐的,仅将“神我”当作一不参与经验世界运行,漠然旁观的他者,是为“完全地不活动”。总此推论,作者说:
为了维持本体至善;朱子的理气论倾向“挂搭”型态;但为了使理具体呈
现于现象,则又倾向“相衮”型态。
由此可见,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之下,理仍是必须参与经验世界的活动,那么,理在这参与现象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活动的可能。[14]
朱子的工夫论与其思想的联结以及实践,同样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雪卿论朱子静坐法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朱子深具儒家色彩的静坐法。所谓静坐,并非儒家本有,此法征于释、老二氏,亦多有所见。朱子对于静坐工夫的认识,则主要来自于二程。作者认为,对朱子而言,静坐法虽非儒门之本质工夫,但却是重要的工夫。也因此,他必须鉴别儒门静坐法与二氏之异同,如不效法佛教坐禅时的趺坐,亦不从道家静坐的数息之法,因为在朱子的认识当中,儒家的静坐不需刻意强调坐姿与调心、气之法,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坐。因此,作者更进一步地指认出,朱子静坐法的特色,其要有二:首先,是将静坐收摄于“主敬”之工夫下,强调“事”,“事”来应事,无事则静坐,敬贯动静,将“主敬”之工夫运用在“事”上。其次,朱子对禅宗顿悟说提出批判,反对其顿教“直证心体”“逆觉体证”等类的心学工夫,他所肯认的静坐法乃是在“格物穷理”工夫中扮演辅助性的角色,故而又常与读书一事对举。据此而言,作者总结出,朱子工夫论中的静坐法应该是“涵养本原”工夫,且朱子的静坐法与他所主张的“格物穷理”关系密切,此则可与道理、读书等诸事并举。[15]
朱子礼学的形成,与其理学体系可谓是互相辉映。冯兵认为,此两者的会通可以自三个层面进行观察,他在文章的摘要中便如此说明:“朱子礼学的情感性维度主要展现了儒家理学重视情感体验的人文关怀精神,宗教性维度显示了朱子礼学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过程,而实践性维度则标明了朱熹对礼学实践的现实有效性的关注。”作者在情感性的论述当中,指摘出如妇女改嫁等问题,以昭示朱子理学的核心价值;其次,在宗教性,则以鬼神论为讨论重点,尽管朱熹的礼学中同样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足以构成为宗教体系;最后,于实践性的探究中,作者指出,朱熹礼学的实践系根据前述的情感性与宗教性叠加而成,此两者虽看似矛盾、难以融洽,却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到有效的会通。[16]
(二)“四书”与经学相关研究
有关“四书”与经学相关研究,计有姜龙翔《论朱子诠释<国风>怨刺诗之教化意涵》、劳悦强《<论语><先进>篇“屡空”辨》以及陈逢源《从五贤信仰到道统系谱—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圣门传道脉络之历史考察》三篇文章。
姜龙翔的论文谈及朱熹对于《诗经·国风》的诠释,尤其是重点关注了所谓的“怨刺诗”。作者指出,朱熹基本上没采用《诗集传序》的持论,将《国风》仅看作是讽刺时政之作,朱子对于《诗经》的诠释,主要关注它的教化功能,因此,他将《国风》视为性情之作。盖《诗经》所录之《国风》,其所载言,主要是人民真实心声的吐露,故有益于为政者的执政参考,着实有重大的意义。总此上述的分析,作者指出,朱熹对于《国风》中怨刺诗的诠释大抵可以得出两种结论:其一,朱子在孔子既有的“《诗》可以怨”的原则下,更加发挥了“怨而不怒”“怨而能正”来补充对《国风》的认识;其二,朱子不采《诗集传序》所论,乃是为避免读者误解《诗经》原本讲求教化、温柔敦厚之旨意。[17]
宋儒治经典之时,其态度多趋向疑经,甚或有改经之作。劳悦强一文,则是从经学史、思想史以及文献学等脉络来对朱熹于《四书集注》中的解释提出质疑。作者的重点聚焦在朱子对《论语·先进》中孔子论颜回“回也其庶乎,屡空”这句话的理解上。其中,“庶乎”为“近道”之义,此系学界公认之通说,殆无疑义。问题主要出在对“屡空”的诠解上。作者指出,自汉代以降,“屡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遵循汉儒所言的“空匮”,二则是何晏(195?—249)别开生面的“虚中”之说,何晏虽别立新说,但他同样循汉儒主张的“屡空”,并以“虚中”为另解,即两者并存。相对而言,在朱子《论语集注》成书之后,其对“屡空”之解,采“空匮”解义,却反倒排斥何晏“虚中”之解,原因在于,朱子指“虚中”为“老氏清静之学”,进而加以批驳。总此推论,作者认为,若依照朱子的解法,基本上并不符合孔子于《先进》篇中所欲阐说的原旨,且朱子更是误解了何晏“虚中”的寓意。[18]
儒家讲求圣贤系谱的传承,主要自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始,到了唐代韩愈(768—824)又有所发挥。陈逢源一文则是在处理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当中对于道统系谱的重新确立。北宋时期,士大夫对于儒门道统传承的看法多受韩愈的影响,并认为孟子得到表彰是受到韩文公重新订立道统系谱的影响,是以,孟、韩二人经常为士人所并举。孟、韩之后,又增列荀子(前313—前238)、扬雄(前53—18)、王通(584—617)三人,于此便形成五贤信仰,五贤信仰又以石介(1005—1045)的推崇为甚。然在王安石(1021—1086)主政之时,完成了一系列孟子的升格运动,使孟子得以配享孔庙,遂脱离了原有的五贤信仰。作者认为,尽管王安石对于尊孟有功,但就他对孟学的理解,尤其对“性善”之体认不深,以致变法失败。然这样的反省其实早在二程时即已提出,二程列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儒门的传道系谱,认为唯有重视性善才是儒学的价值核心,但终北宋一朝仍是不脱以五贤信仰为主,直到宋室南迁这一变局形成之时,方才刺激士人对道统系谱进行重新思考。作者指出,南宋对道统重新提出认识的,当以朱子为集大成者,朱子自儒门经典中重新寻求答案,终于在《中庸章句序》得出答案,揭示“尧、舜、禹、汤、文、武圣人相承结构中,续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传道系谱,彰显儒者遥契尧、舜,志继孔孟的情怀”,此为后人所周知的道统系谱,足见历代道统的积累,主要亦是根据朱熹建构的成果。[19]
(三)朱子的史观与史学
本年度讨论朱子的史观及其史学的研究,计有胡元玲《朱熹对宋王朝南渡变局的省思》以及黄俊杰的《儒家历史叙述的特质:朱子历史叙述中的圣王典范》《儒家历史解释的理论基础: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三篇专论。
综观朱子生涯,多是从事讲学,于乡里之间活动,但这并不表示朱子就此与政治无缘,《宋史》载朱子一生立朝仅四十余日,但这并不妨碍朱子本身对于政治的观察,至少就宋朝当代的历史是如此。胡元玲一文即是从宋王朝南渡的历史事件来考究朱子的省思态度,主要从朱子对于宋代历史(评论徽宗、钦宗北狩;批评高宗南渡与建都;批判秦桧误国以及陷害忠良;检讨隆兴北伐与和议;维护正统立场等)的观察来展开论述。据此,作者认为,朱子在“内圣”讲求遥契圣贤的修养层次,其造诣固然可观,然就“外王”而言,亦多可见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20]
朱子除了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观察外,他更将这种眼光投注于历史的发展,黄俊杰一文,则是试从朱子的历史论述中爬疏他的圣王典范。作者指出,宋儒的历史论述中,多是透过特定的史实来进行叙述,借以提炼事中之“理”,而这些“理”则泰半呈现在圣人的行谊之上,因此,就以宋儒的史识而论,朱子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朱子认为挖掘史事中的“理”必须先阅经典,次阅史籍,作者在统括这段认识后,进行如此诠解:
朱子之所以说“经”比“史”更重要,主要的含义是:读史的目的在于即“事”以穷“理”,史实的究明只是手段,史理的抽离才是目的,而经由抽
离之后的“理”主要见之于经书之中,所以“经”先于“史”。“即史以求理”中的“理”兼具内在与超越等两种性质,故“理”不脱离史实,但又超越于史实之上。最后,作者认为宋儒乃至于朱子历史论述中的圣王典范,其所运用的方法多是“从历史论述提出哲学命题”,从而成为他们的核心价值。[21]
朱熹关于历史的相关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其门人贯彻他意志所撰写,诉诸名分、正统的《资治通鉴纲目》。然而在朱子的其他著作当中,亦可见到一些他对于历史的观察,黄俊杰则侧重研究朱子对于中国历史的诠释。作者首先指摘出朱熹推崇三代的史观,是为“崇古的历史观”,认为自三代以后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堕落的态势,这样的转折主要是自秦代开始,原因在于自秦代所发轫的政治体制,呈现出“君尊臣卑”的关系。朱子的史观聚焦在“势”的转变,如由周至秦的“事势之必变”以及汉晋之间的“因其事势,不得不然”,两者皆然。接着,作者指出,在朱子的认识中,能够驾驭历史之“势”的只有人,因为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作者还通过朱子“理一分殊”的特点来考察他的历史理论,朱子认为历史虽遵循着“理”来发展,但这种“理”的体现只有历代圣贤能够掌握,不免也忽略了群众对于历史的作用。总此论述,作者认为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主要是以三代作为批导现实的精神杠杆,通过理想化的三代来评骘历史,企图将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镕铸在一起,这大概是朱子史观的特色。[22]
(四)朱王比较
朱陆异同以及朱王异同,此间所涉及的经典诠释、义理析论,向来是研究宋明理学重要的议题。而就2014年度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主要有蔡家和《朱子与阳明的孟学诠释差异之比较》以及黄信二《从朱子与阳明论蒯聩与卫辄比较朱王之“礼”论》两篇文章。
蔡家和通过朱熹和王阳明(1472—1529)对于孟学的诠释来展开论述,作者以(1)“尽其心者章”的诠释、(2)孟子学的义内义外问题、(3)性属理还是气、(4)性是善还是无善恶等,作为朱王之间诠释的相异处进行了比较。就(1)而论,作者指出,朱子诠释《孟子》时,主要以《大学》的架构进行通贯,重视先知后行的为学次第;相对于此,阳明则不重为学次第,但同样是以自倡的良知学来诠释《孟子》,据此,《孟子》成了一个过程的工具,朱王只是通过《孟子》来发明自己的学说。就以工夫论一事而言,作者指出,朱子论工夫时分居敬与涵养为二,但阳明的工夫只着眼在致良知一个工夫上,亦不相同。以(2)来说,作者认为,阳明的说法较符合孟子原意,因为朱子的体系扩及到宇宙论范畴的天地万物,故其义在内也在外。关于(3)的课题,孟子本来没有将性分为形上、形下之区别,但朱子因在佛教传入后,容摄其思想体系来开展新儒学,故以理气诠释。就性为理气和这点的说法,朱子较近似于孟子,阳明持论则是弥补朱熹的二元区分。至于(4),作者认为,讨论到性为善或是无善恶的问题时,朱子的诠释较近于孟子,因为阳明将善分为绝对善与相对善,此系儒家在面对佛学问题下,进而抟成的一种思维,可视为阳明自身的创造,但却远非孟子本意。[23]
黄信二一文,则是就朱子与阳明对春秋时卫国蒯聩与卫辄父子之间的王位之争是否合乎礼之准则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从两者释“礼”的差异来进行分析,朱子的立场在于贯彻某种伦理价值,使其合乎礼;阳明则是紧扣着使礼能被彻底执行的道德动机。据此,作者认为朱王之间对于礼之过程的“应用”与“发生”的重视程度,有其不同。以蒯聩与卫辄一案来说,阳明偏重父子之间的感受,故其重视礼“发生”时情感的考虑;朱子则侧重在父子之间的关系,“应用”并严守亲亲义理,借以提炼出某种普世价值。作者指出,阳明认为,应使蒯聩与卫辄相让为国,恢复良好的父子关系,重视人情天理。朱子则认为,蒯聩与卫辄皆不应登位,如此便不会有后来相争王位等事,应重视礼之意志的执行,但更强调其中的节制意义。最后,作者在比较朱王二者后认为,其二人对礼认识的差异仅在于思想体系中对于体用关系的侧重程度不同,并不代表他们的理解有所误差。[24]
(五)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
近年来,汉学研究的崛兴,同时也使得其在域外儒学等相关领域受到重视,就这一点来说,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更是不可忽略的重点,就历年来的研究趋势而言,主要聚焦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2014年度中国台湾学界关于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出版同样丰富,其中尤以韩国朱子学的研究为最多。
1.日本
关于日本儒学研究的文章,本年度业已出版的论文,计有张文朝《渡边蒙庵<诗传恶石>对朱熹<诗集传>之批判——兼论其对古文辞学派<诗经>观之继承》以及傅锡洪《“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探微——有关儒家天人合一之学之建构与解构的一项考察》等。这两篇文章所关注的课题,均是聚焦在古学派对于朱子学的批判上。
就日本汉学的发展来说,因其特有风土环境、政治思维的影响,从而长成的古学派,他们所欲申阐的论点,主要关注点在对朱子学的解构上,其中又以荻生徂徕(1666—1728)的萱园学派(古文辞学派)影响为大。张文朝一文的切入点则放在萱园学派的渡边蒙庵(1687—1755)对于《诗经》的诠解上。盖渡边蒙庵主要师承太宰春台(1680—1747),又为荻生徂徕之徒孙,是以,就他的《诗经》观而言,同样深受两者的影响。作者以蒙庵的《诗经恶石》为分析文本,并指摘出它非但不是如历来研究所指认,为其师春台《诗经膏肓》的补注,反而能从其中窥见古文辞学派中治《诗经》的态度以及对朱子的批判。不论是春台的《诗经膏肓》,或是蒙庵的《诗经恶石》,基本上都将《诗经》视作一部诗选。作者认为“古文辞学派学者大多有挟汉儒去古未远之势,以制朱熹新注之说的倾向”,故此,从徂徕到春台再到蒙庵的一贯立场,均在取消《诗经》的经书地位,并通过学习《诗经》中的古文辞、掌握个中揭示的人情,以供施政之用。此举主要是以“知人情”来供为政者参考,不若朱子以《春秋》的“劝善惩恶”来阐释《诗经》。再者,古文辞学派认为经典为圣王之作、安民之道,故其重视实学层面,这也是为什么蒙庵要批判朱熹以持敬、义理、治心来解《诗经》,因为此并无助于现实政治治理的需要,是为无用之学。[25]
相较于对经典诠释的批判,古学派于思想体系对朱子学的解构,亦有所见。傅锡洪就朱子的鬼神观来考究它的成立,以致后来儒学东传日本后,遭到江户时期古学派彻底解构的过程。一般而言,常人多将鬼神析分为二,其一为“在天之鬼神”(即阴阳造化),其二则是“祭祀之鬼神”(即神示祖考),但朱熹认为,在儒家经典中,此两“在天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是统一的,而非“二事”。若鬼神是“二事”,则人道不能本于天道,儒教的天人合一之学将由此被截断。然这样的认知来到日本,力图解构朱子学的古学派学者,便严分鬼神祭祀与现实人世的距离。作者指出,古义学派的伊藤仁斋(1627—1705)首发其端,他并不否认阴阳之鬼神,却也不谈及祭祀时的鬼神感应,对于鬼神是否为“二事”采“不必”的立场。古文辞学派的荻生徂徕,同样反对鬼神感应之说,对仁斋之说亦提出批驳,因为他认为鬼神并不可知,只要遵循先王之道即可,他对鬼神的认知仅限于天神人鬼作为祭祀对象的鬼神,反对形上的阴阳造化,因此,就鬼神是否为“二事”而言,他采“不能”的立场。怀德堂的中井履轩(1732—1817)虽不否认阴阳鬼神之存在,但就祭祀而言,他认为鬼神“不在”,重要是己身的孝敬之心。于此,朱熹所持论的“在天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并非二事,在江户中期开始受到古学派或批判、或痛诋,终将其彻底析解为二。[26]
2.韩国
韩国儒学的发展,自进入朝鲜时期(1392—1910)后,即已确立以朱子学为国学,将其定为一尊,故有关朝鲜时期的儒学研究,多是指向以性理学为宗的相关研究,讨论的重点亦多是围绕在对朱子思想的诠释上。就本年度的韩国儒学研究而论,有姜真硕《栗谷哲学与人物性同异论之成立》以及李演都《湛轩洪大容的“人物均”论探究——朝鲜后期人物性同异论争的演变与其意义》等讨论人性、物性同异论的专文,另有姜智恩《东亚学术史观的殖民扭曲与重塑——以韩国“朝鲜儒学创见模式”的经学论述为核心》一文,则是尝试梳理20世纪初韩国学界对于17世纪朝鲜儒者思想世界的过度扭曲,借以廓清对朝鲜学术史观的认识。
韩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两大论争,其一为“四端七情论争”,其二则为“湖洛论争”。湖洛论争,主要是湖学与洛学两个学派对于朱子学诠释的不同立场所产生的,而人性、物性同异论便是两派论争的主流。姜真硕一文即揭示了人性、物性同异论争,其实与李珥(号栗谷,1536—1584)的哲学思想诠释密切相关。即在此议题上,栗谷哲学居其中心的地位。作者认为,16世纪由栗谷提出“理发气乘”和“理通气局”建构己身之哲学体系,且其中的“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成为17、18世纪栗谷后学开展人性、物性同异论争的基本骨干。作者指出,栗谷及其门人都着重在探讨气的思想,“气局”突显了他特有的思维。栗谷认为,人、物之不同除了表现在气质外,其理禀亦不相同,故说万物“不能禀全德,心不能通众理”。而就气禀来说,作者认为:“人不能不有气质的限制,而同时具备虚灵洞彻之心,因此能够克治气局限制,变化自己。”因天生气禀之有别,是故人有圣俗之分。由此观之,栗谷之“气局”说不但证明了人性、物性之有别,更进一步地阐说了人、人性的异论。[27]
如果说人性、物性同异论争是以栗谷的哲学思想为肇端所产生的,那么,这种论争的转折则主要可自洪大容(号湛轩,1731—1783)谈起,李演都的研究即关注于此。作者指出,在18世纪初湖洛论争进入高峰期时,正好是洪大容活跃的时期,而此时朝鲜性理学的发展,已然走向在理学、心学的基础上,同博学结合的趋势。湛轩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故其重视实学,是以,就他所主张的气论而言,他主要只以气之活动来阐释宇宙的形成与变化,并且对朱子学中理之主宰性提出反驳,但并不反对理的存有。作者指出,湛轩思想中理的地位主要是:“基于对于自然界的经验上之普遍原理。”此气一元论的立场,系湛轩理解人物论的重要前提,作者通过湛轩在《医山问答》中的《人物心性论》以及《心性问》《答徐成之论心说》等文,揭示了湛轩讨论心性论的关键词,乃在“以天视之”和“人物均”。就前者言,湛轩认为要“以天视之”,方可超越“以人视物”“以物视人”两种观点。至于后者,作者则指出“人物均”的概念与湛轩之气论息息相关,湛轩持气一元论,故其认为心亦是由气构成,但湛轩认为人性与物性在心的本体上并没有区别,即他主张的“人物心本同”,扩张洛学本有对心论的认识。至此,作者指出,湛轩已然摆脱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价值,且他是“站在物活论的自然观之立场来看待人与物的同等关系”,此举近似于现代以科学角度来对自然万物进行观察,同时也开启了朝鲜后期性理学的转向。[28]
朝鲜王朝可说是以朱子学立国的政权。但是,将朱子学定于一尊的影响,并不止于学术层面,在政治场域亦有所见,如国家政策、礼制亦多遵照朱子的训示。而在日本殖民时期(1910—1945)的韩国学界,则认为韩国之所以沦落于此,应该要彻底批判将朱子学定为国学一事。但这样所谓“彻底批判”并不免启人疑窦,且有失其学术观察的客观性,姜智恩即尝试就东亚来作为观察视域,借此重构17世纪朝鲜经学史的图像。作者指出,日本殖民时期,日本的御用学者(如高桥亨、井上哲次郎等)多是贬低朝鲜儒学,指其缺乏创造性,不若日本江户时期之古学对朱子学提出挑战,直接迈向近代化。是以,就20纪初期的韩国学界而言,有鉴于过度提高朱子学地位进而导致亡国,故当时的知识分子多采取以下两种策略:“其一,是批判只信奉朱子学的儒家,其二则发掘‘非朱子学’的历史人物,来作为‘近代先驱’而加以赞扬。”以此来反击日本官方的论述,作为拯救国难的新的学术史观。作者在梳理、比较日本御用学者与韩国学界的论点后认为,20世纪初以如此“矫枉过正”的态度来批判朱子学,其实并无助于理解17世纪时儒者的思想世界,其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的儒学发展模式不同。日本为武士政权,故重武治,且并没有施行科举,儒学的影响性并不大,相对于此,韩国则是重文治,以科举取士,儒学(朱子学)的影响可谓是十分深刻,即使无官职之士人亦可对国政提出谏言。因此,以日本经验来贬抑朝鲜儒学,恐怕不能成立。再者,作者指出,朝鲜的儒者并非完全尊奉朱子学,他们亦自朱子矛盾之处,提出独创的见解,并找出朱子另一说法并陈,此即作者定义的“朝鲜儒学创见模式”。准此,17世纪时朝鲜的学术空气并不如20世纪初学者所认为的“盲从朱子学”或是通过“批判朱子学”进而得到更新,相对地,反而是更加仔细钻研朱子学,始能具其新的诠释。如此,作者认为,必须重新正视朝鲜儒者对于朱子学诠释的独创性,以免走入被扭曲的经学史观当中。[29]
综观本年度中国台湾学界关于朱子学的研究,由于国际研讨会的举办、学术期刊推出朱子研究的相关专辑,甚至于学术交流的增加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说是十分丰硕。本年度朱子学的研究议题,除了对于朱子学术、思想观念提出新的见解外,亦旁及他的史观、史学以及“四书”学等,甚至与阳明之间进行比较,总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都丰富了对朱子学的探掘,使吾人能一窥堂奥。
近十多年来,台湾地区的儒学研究开始尝试以东亚作为视野,借此视角来观察儒学于东亚世界中所呈现的多元样貌,这其中尤以朱子学的影响最为深刻。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展开,此似可援引黄俊杰教授借朱子“理一分殊”的论述来加以阐说。[30]即将中国原生的朱子学比喻为“理一”,将域外朱子学视为“分殊”,并自“分殊”之中觅得“理一”,相互呼应,产生对话、交流的可能性。我们亦可从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中,窥见这些存于域外并且生机盎然的思想体系。如日本古学派(古义学、古文辞学)对于朱子学的解构,他们讲求实学,反对形而上的“理”,在日本的风土环境下证明了已有的思维系统。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的是,本年度有关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数量明显增多,尤其以朝鲜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最多,他们主要通过会议论文、期刊论文的形式被介绍到中国台湾学界,从而充实了对韩国儒学的认识。如前述提及湖洛论争当中的“人物性同异论”,以及姜智恩论述下的“朝鲜儒学创见模式”等学术史的发展,均是在朝鲜特有的历史环境下所成形的。
总括前述所论,我们可以从朱子学在东亚世界遭受到不同的际遇,来重新审视各个政权、文化体系之间对于儒学受容的影响(诚如姜智恩一文所揭示的),亦可通过此一比较来反思中国原生朱子学,乃至近世以降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整体构造,以为他山之石。尽管对中国台湾学界而言,东亚朱子学的研究呈现逐年增加之势,但唯一可惜的是,本年度并没有针对越南朱子学进行专门探讨的论著。
2014年香港朱子学研究综述
——以“朱熹与宋明理学”研讨会为焦点
吴启超
2014年12月4日至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次“朱熹与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会议云集中国、韩国、新加坡的朱子学专家学者共21人,发表论文20篇(其中一篇由二人合撰),可谓去年香港朱子学界一大盛事。本文将介绍评述当中几篇由香港学者发表的论文,让读者了解过去一年香港朱子学研究的进展及其今后的动向。
与会者中,有三位在香港的大学任职,包括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陈荣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吴启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此外亦有三位出生于香港而现正任职于香港以外的大学,包括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杨祖汉(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劳悦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以下依次介绍这六位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和观点。
(1)郑宗义教授为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现任主任,发表论文题为《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众所周知,当代新儒家牟宗三(1909—1995)的朱子哲学诠释既体大思精又别树一帜,其由仔细的文献梳理和精密的理论剖析而得出的论断,例如指朱子为“儒学之歧出”“道德之他律”“泛认知主义”等,至今仍为学界所热议。郑宗义一文则提出,同属当代新儒家的唐君毅(1909—1978),其朱子哲学诠释散见于《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书中,论述之集中程度及篇幅或不及牟宗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则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手的诠释体系”。是故,该文即旨在“通过比论唐、牟对朱子哲学的不同看法,来将唐氏提示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发挥与建构”。但作者随即强调“比论之意义,固不在分辨高下,而是在于能对朱子哲学更求善解”,表示该文所从事的乃客观持平的学术工作,而非为争门户。
笔者理解,郑教授一文的关键议题为“朱子哲学能否承认‘心体’(‘心’本与‘理’为一)之观念”(牟宗三对此持否定立场)。若能,则朱子之“心”自非如牟宗三所理解般,纯然只是一“认知心”,而其理论亦非如牟氏所指,为“泛认知主义”(以“认知”决定“行动”)并存在“道德动力不足”的困难(仅靠“格物穷理”的认知工夫不足以推动道德实践)。再者,朱子哲学中一些重要概念如“敬”“真知”等,亦将可得一既有别于牟宗三而又更为妥善的诠释。换言之,“论证朱子哲学有一‘心体’之观念”可说是全文立论之基石。
为此,郑教授详引唐君毅文字,指出唐氏肯定朱子有“心体”之观念。更重要者,郑教授并非仅仅引录复述唐氏之言,而是进一步通过朱子原文来为唐氏的诠释予以补充、强化和证明,使得全文读来持之有故,推论稳健。可是,会议上亦有学者提出疑问:首先,唐氏固然有使用“心体”一词,但其用法是否同于牟宗三,指一“本与‘理’为一”的“心”?其次,郑教授虽然提出朱子有“介然之觉”和“立志”等说,以证明朱子确可安立“心体”之观念,但正如牟宗三曾指出,朱子立论常有些“不自觉的因袭语”——不自觉地因袭儒学传统内(尤其孟子)的用语,因此,“介然之觉”“立志”等语,从朱子口中说出来,其真实意义到底如何,恐怕仍需穿透字面而做进一步的解读。但话说回来,郑教授一文虽仍有可议之处,然其试图立足于唐君毅而建立一套完整而周延的朱子哲学新诠释,实亦为朱子哲学研究之另开新局踏出了一步。
(2)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荣开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朱子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环绕其<四书>解说所作的观察》。全文长达41页,极具分量,以朱子的《中庸章句》第二十三章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为焦点,进行了非常细密的剖析,可谓强探力索。笔者撰写本文前,曾与陈教授通信,得知该文乃其有关朱子《中庸》注研究的延续。该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目的乃在剖析《中庸章句》所强调之严密结构,从而揭示其中未为熟知的义理内涵。陈教授并向笔者表示,该研究目前尚在推进当中,待他日把计划内的文章写就之后,将汇辑成编,以便学者参考。以下即此项计划所已发表的论文:
①《朱子<中庸>首章说试释》,收入《结网篇》,1998年,第407—488页;
②《读大槻信良氏有关<中庸章句>典据的研究》,收入《结网二篇》,2003年,第495—530页;
③《朱子<中庸>结构说(上)》,收入《儒学、文化与宗教——贺刘述先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2006年,第63—96页;
④《朱子<中庸>结构说(中)》,收入《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2009年,第429—468页;
⑤《首尾接续,血脉通贯——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章缜密结构的分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五辑,2009年,第151—184页;
⑥《朱子对<中庸章句>“诚明”章的剖析与解读》,收入《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1年,第610—624页;
⑦《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的解读》,收入《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第208—232页。
回到陈教授此次会议发表的文章。该文聚焦于朱子对《中庸》第二十三章首句“其次致曲”的解释:“‘其次’,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故题为《朱子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陈教授亦表示:“为了充分掌握朱子对此句经文的理解,本文又大幅引用了他对《论语》《孟子》等书有关篇章的解释。”是故该文在正题之下再加上一副题:“环绕其《四书》解说所作的观察。”
依笔者理解,陈教授一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探讨“致曲”这种属于“大贤以下”之修养工夫的背景、目标和依据。“致曲”的背景就是人的“天性”与“气禀”:凡人皆有纯粹至善的“天性”,唯其落实于人身,即不能不受“气禀”的干扰(尤其是“大贤以下”之人),而有种种“曲”的表现。目标方面,“致曲”的进行有两种向度:“量的向外推展”(把“善端”横向地推展至生活上的时时刻刻)和“质的内在提升”(把“天性”之呈现趋于精纯,愈来愈摆脱“气禀”的夹杂)。陈教授认为,两者相较,后者更属“致曲”工夫的重点。依据方面,整个“致曲”工夫的历程,不论是起点(察识善端)、归宿(善端之充满)或其间的过程(善端之推扩),无不以本然内具的“天性”为依据。
第二部分,陈教授集中讨论朱子眼中“气禀”在修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根据相当充分的朱子原文(尤其是朱子对《论语》《孟子》的解释),表明朱子对“气禀”之于道德修养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有非常深刻的照察,例如令人在道德实践时产生潜在于隐微之间的不纯意念、令人知而不行(明知其是或非,却又当为而不能为或当止而不能止)等。但另一方面,陈教授又指出:“尽管如此,朱子之以气禀言曲,实也反映其不以气禀为全然的不善。在他看来,天性的展现固不可能离乎气禀,作为天性得以体现的载体及其所能充扩至极的据点,气禀更有其积极的意义。”
(3)笔者本人于此次会议交出了《是非之心在朱子哲学中的特殊性》一文。拙文“尝试揭示朱子对于‘四端之心’中的‘是非之心’的特殊看法,进而指出,我们若能注视这点,将可对朱子的某些论述(尤其工夫论)、立场和论证得到更好的理解,亦可更准确地测定朱子哲学所可能触及的某些哲学议题”。拙文因而分为两部分,先讨论朱子对“是非之心”的特殊见解,继而探讨:“基于这种见解,朱子在工夫论上可以对其儒学内部之论敌(本文将以湖湘学派为例)提出怎样的质询,以至当中可能触及何种哲学议题。”
所谓“朱子对‘是非之心’的特殊见解”,拙文提出两点:第一,在朱子,“是非”与“恻隐”“羞恶”“辞让”不同,本身可能不是一种道德情感。“我们或许会由于朱子以‘情’概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太快地以为此四者皆一概属于‘情感’(emotion)。”但拙文试图指出:在朱子的用法里,“情”不必皆指“情感”,而且“在朱子的论述里,‘是非’跟‘恻隐’‘羞恶’‘辞让’有着明显差异,其情感性格并不突出,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反而,当他描绘‘是非之心’时,却处处强调其‘分别是非’的认知或判断作用”。第二,此“分别是非”之功能,还只是一个比较表层或宽松的提法,更准确地说:“依朱子,‘是非之心’的真正重要的作用,是‘识是非之所以然’”,即“识别是之所以为是或非之所以为非的理据”。简言之,朱子的“是非之心”更应当被理解为“识是非之所以然”的作用,而非一种道德情感。
拙文第二部分进而讨论:“当我们掌握了朱子的‘是非之心’的上述特性后,我们在理解朱子在某些哲学议题上的立场和论证会得到什么帮助?”笔者于是以工夫论议题为例,探讨朱子对湖湘学派的“识心”工夫的反驳,并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朱子与湖湘学派的切磋,带入情感哲学(philosophy of emo-tion)的领域里。”换言之,准确掌握朱子“是非之心”的特性,对于深化宋明理学内部的哲学讨论,以及将这些讨论带入普遍哲学议题里,实有明显的帮助。是故,拙文总结道:“我们对‘是非之心’在朱子哲学中的特殊性(情感性格不明显、以‘识是非之所以然’即‘理由探问与提供’为其根本功能)应予注视,因为这样做将会更深入地理解朱子在某些哲学议题上(例如工夫论)的立场、思路和论证,甚至可以做出朱子所可说而未说的理论推演(例如有关‘识心说’的争议),以及测定朱子哲学所可能涉及的普遍哲学课题(例如情感哲学)。”
(4)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李瑞全教授发表了《朱子论心体的纠结历程:朱子早期之工夫论奋斗》。该文从北宋儒学的工夫论谈起,作为朱子于工夫体悟上之纠结历程的背景,一路谈到朱子从学于李侗(延平),却又不能接上其师的经过。全文辨析精微,尤其对《延平答问》里朱子与李侗之间种种往来讨论有极仔细的剖示,清楚阐明朱子如何曲折地走入理学语境、终又接不上程颢至李侗一脉之情形。
文中有两点特别令笔者受到启发。首先是作者认为“朱子之困扰实因成圣工夫自明道之兴发之后,实蕴含了一内在的实践上的循环(practical circle)”。其后,作者更进一步将此“循环”具体定性为“工夫实践之循环”(practicalcultivation circle)。宋代理学自程颢(明道)开始,工夫论(修养方法之理论)议题逐渐明朗起来。明道重在点出圣人境界,提示出一基本的工夫方向。其弟程颐(伊川)则更着手于具体工夫操作之开发,从而提出以“敬”涵养“未发”之一路工夫。然而作者本乎唐君毅之见,指出此路工夫实有一种困难:心体未发之时,一无所显,故无所谓“涵养”——要涵养也不知涵养什么,以其未显任何活动故;可是,“涵养”之工作一旦发动,则又已然进入“已发”状态。这就显出一种永在追逐而其目标——未发——又永不可即的“循环”况味。作者的见解虽说本乎唐君毅,唯其首倡“循环”一词以描绘个中情状,亦确然为前人的观点做了精到的概括。
其次,正如刚才提到的,李教授一文对朱子与李侗之间种种往来讨论有极仔细的剖析,清楚揭示了两师徒间隐微的义理分歧,这里稍举一例。对于朱子与李侗就孟子论“夜气”一章的讨论,李教授先言简意赅地点出:“延平教以持守此平旦之气,即是持守孟子之本心。”继而分析道:“孟子虽说有放心之时,但本心并不真是丧失掉,实只是此心被遗忘,被物欲所掩盖,宛若不见而已。由上可见,延平所教是持守此本心,涵养即涵养此心,而非如朱子引用伊川之以持敬致知的方式去涵养心体。由此可见,朱子此时实未能了悟二程之学,常有此种执实语句文义而不通透的论述,故延平亦常戒以如实平观前贤之说,不宜妄为比附之言。”如此细腻的剖析,让读者对朱子如何跟其师李侗,甚至程颢学脉最终分道扬镳,有一扼要的认识。
(5)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杨祖汉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
笔者观察所得,近年汉语学界(尤其香港、台湾地区)从事朱子哲学研究者大多以牟宗三的朱子诠释作为参照坐标,不论赞成还是反对牟说皆然。在此共同背景下,研究者所走的方向约有两种:或致力在牟氏诠释以外,另立一套更为妥善的朱子诠释;或大体接受牟氏诠释,而在牟氏之个别论断上提出异说或修正。前文介绍的郑宗义教授和以下即将介绍的杨祖汉教授,便恰好分别走了上述两条路。
杨教授近几年发表的朱子哲学论文,均在牟氏诠释的基础上,对牟氏之各种关于朱子哲学的评断予以再思。就是说,对于牟氏的很多主要诠释,例如“心性情三分”“心不即是理”等,杨教授均大体接受;而对牟氏的很多论断,例如“朱子之‘心’不能提供充分的道德实践动力”等,则进行重检。此次会议,杨教授即针对“道德实践动力”一课题,借助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之论尊敬,来揭发朱子“敬”论中的深层意蕴,试图论证朱子之“敬”论亦能在心学路数(主张“心即理”)以外对道德实践动力提供一种站得住脚的说明。全文结构与思理严整,推论步骤稳健。杨教授兼擅儒家与康德哲学,讨论起来自然出入无碍、左右逢源。
该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步骤,可借文中三段文字概括表述。首先,“朱子不主张‘心即理’这是很确定的,但心不即理并不表示理不能本在心中,吾人可以在心即理与心是气的区分外,说心虽不即是理,但心亦非只是气;即虽说心不是理,但心中有理,心本知理。即表示在人的现实经验的心灵主体中,虽然心不是理,但也不能说心对于理完全无知”。其次,所谓“心本知理”,此“理”即指“道德法则”而言,于是:“(……)了解什么是道德法则,就会承认法则对于意志能够直接地决定,而可以单因为法则的缘故而行,不为任何其他的动机(……)。要求人要无条件地只因为理的缘故而行,这种要求当然就是一种实践的动力。这是由认识到纯理而产生的动力,这一种动力可以只因为对于理的认识而产生,不必如牟先生所说,本心呈现才可以给出实践的动力。”最后,“以上运用康德论尊敬之意,阐释朱子也可以有因明理而生敬,因面对道德之理感受到理的庄严而又觉得自己现实生命不如理之纯粹,于是产生戒慎恐惧之情,从此一角度来看朱子的敬论,应该不算比附”。
(6)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劳悦强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以表证里——漆雕开与朱子的道德诠释学》。劳教授以其一贯敏锐的文字触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论语·公冶长》‘漆雕开章’,其中漆雕开回答夫子曰:‘吾斯之未能信。’原文并未直言‘斯’字的指谓,朱注则曰‘指此理而言’而并未提供训诂证据。再者,本章简短,才十六字,所记有限,而《论语》全书又仅此一章言及漆雕开,文献似不足征,然则朱熹如何诠释此章,从而洞悉漆雕开的道德修养境界,实在值得深究。”文章旨在剖析朱子“以表证里”的诠释手段及其所凭借的格物致知立场,务求通过朱子这位理学集大成者,展示理学本身的经典诠释风格。
该文首先借汉儒旧说,厘定“漆雕开章”的本意。劳教授说:“漆雕开所未能信者并非出仕时机是否适当,或应否出仕,甚至也非他对出仕之道尚有未明之处;他未能信者乃他本人的学问和本领。汉孔安国认为,漆雕开之所以未能信者,因为他‘未能究习’仕进之道,可谓切中原文意指。”接着,劳教授通过阐述张载与二程对此章的诠释,以表明朱注的理学渊源和基础。然后,文章便正式进入朱注之剖析。劳教授扼要道出了朱子的诠释原则:“原则上,朱熹解读《论语》文字就是结合外在讲究与内在经验的道德诠释,一方面强调实证的文本细读和入微的义理剖析,另一方面又玩味体认义理的主体之内在存养功夫及其气象。”简言之,对朱子来说,诠释经典,既要观言(细读经典文字),也要观人(玩味体认言说者的气象)。劳教授更从《朱子语类》卷二十九中拈出朱子“以表证里”四字,作为这种诠释风格的概括性表述。所谓“以表证里”,就是从言说者的外在表现(语言、行动等)证知其内里的整体人格和修养,从一事而见其全体。
然而,文本的“表”是有目共睹的,但要如何才能穿透文字的“表”,通达文本之“里”?这就得靠诠释者本人经过格物致知而得出结论了:能格物致知者,自能对“斯理”有深刻的体认,继而能以“斯理”去测定文本之“里”。但反过来说,阅读经典亦正是磨炼吾人明了“斯理”的途径,而为格物致知之一端。是故,劳教授在文末总结道:“解读文本自然不是一个道德行为,而且文本的内容也不一定与道德有关,但对朱熹而言,解读文本是一个格物穷理致知的活动,而所谓‘理’则寓藏于客观事物之中,因此归根究底,文本诠释自然以‘理’作为终极的义理参照。(……)一旦文本涉及人事上之‘斯理’以及其所有相关节目,朱熹便极力讲究读者与文本之间在‘斯理’上之默会体察,因为经典所载就是圣贤体验‘斯理’的记录。(……)因此,读书并非纯粹的所谓客观认知活动,而更重要的是读者借助书册上的文字,与圣人以心印心,从而体验‘斯理’。”
以上评述了会上六位香港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和观点。虽然当中只有(1)(2)(3)三位在香港任事,但广义而言,(4)(5)(6)三位亦可算入“香港朱子学研究者”之中。总括来说,在香港,朱子学的研究风气相对其他地区来说不算盛行,但其研究的路径却颇为多样:有对朱子文字做微观细析者,如(2)(6),有对朱子本人的思想进展做追踪描绘者,如(4),有对不同的朱子哲学诠释做比论者,如(1),也有致力将朱子哲学带入普遍哲学议题之讨论或比较哲学之视野者,如(3)(5)。可见人数虽少,却颇具活力;今后通过持续与其他地区学者的交流互动,可望不断推进香港朱子学研究的成绩。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2013—2014年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刘倩
在2013至2014两年间,美国有关朱子学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发展。虽然相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其著作、文章的数量并非蔚为大观,但其研究质量与成果值得学界了解和重视。本文即为一篇按专著、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这一顺序对近期美国朱子学研究情况加以介绍的文献综述。[1]
学者艾周思(Joseph A.Adler)于2014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Dao:ZhuXi’s AppropriationofZhou Dunyi)是一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专著。[2]学界长久以来多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朱子的思想,然而,艾周思在这部专著中却从宗教实践的角度详细讨论了朱熹如何运用周敦颐的思想来进一步发展儒学。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于上述观点议题的讨论分析,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对重要文献的翻译。
在第一部分中,艾周思一方面探讨了周敦颐在朱熹的道学谱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也细致讨论了朱熹如何运用周敦颐的思想,并解释了周敦颐思想当中某些概念的意思。艾周思首先描述了朱熹所建构的道统,认为根据朱熹的观点,这个道统在孟子之后便中断了超过一千年,而接续这个道统者应为北宋之周敦颐而非后来的二程。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朱熹认为周敦颐和伏羲一样,在没有任何人的指导下便能全面地理解“道”。不过,艾周思也同时指出,朱熹视周敦颐为圣人之道的接续者,这种观点在宗教、哲学和历史三个方面都造成了若干问题。在肯定了周敦颐在朱熹所构筑的道统之中的地位后,艾周思继而讨论了朱熹如何利用周敦颐“动静互通”的思想来作为其自我修养的方法的基础,借此处理他在1160年所面对的思想危机。此外,周敦颐最重要的思想为“太极”,艾周思在最后主张应以“Supreme Polarity”而非“SupremeUltimate”来翻译“太极”一词。他解释这样翻译的原因,是因为“太极”虽是一个终结,但同时亦是一个转折,故“Polarity”能更好地表达这重意思。而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艾周思则翻译了周敦颐一些最为重要的著作,朱熹对于这些著作所做的注释以及朱子和其门生对于这些著作所做的讨论。
除了艾周思有关朱子学的专著以外,贾德讷(Daniel K.Gardner)在撰写《儒学简介》(Confucianism:A Very Shortlntroduction)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的著作时亦用了一章的篇幅简单介绍了朱熹的学说。[3]作者认为朱熹或许是当时众多理学家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并分别描述了他有关“理”与“气”的形而上哲学,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自我修养功夫、步骤和方法等。
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学者也发表了若干讨论朱子学的论文。田浩为当今美国朱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自2012年其著作《旁观朱子学》出版以后,他撰写了多篇论文继续探讨朱子学当中的议题。首先是他与现为普渡大学助理教授的女儿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共同撰写的《儒家婚礼之重构与现今中国青年文化:援引经典以回应棘手问题的案例》一文。[4]朱杰人和张祥龙这两位复古派学者为了提倡并恢复传统仪式与文化,故各自为其儿子策划并举办了儒家婚礼。而此文则深入分析了这两场婚礼的社会意义,以及两位学者如何将现代元素融入两场婚礼之中。同时,它亦探讨了两场婚礼的具体差别。为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两位作者还特意访谈了参与者,论述了其他学者对这两场婚礼的评价。在文章中,他们认为从恢复古礼以及让参与者明白古礼的价值方面来看,两场婚礼都是相当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2年,田浩与田梅就此议题,还共同合作撰写了《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这两篇文章无疑都是对儒家婚礼与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积极探讨。
同时,他亦曾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一文。[5]该文从礼理的关系讨论了宋代经典转型的问题。两人指出“五经”和“四书”都是以“礼”为中心的,但后者对于“礼”的发挥则比前者更为集中,且更关注于“宇宙论”及“心性论”,故此宋代之理学家渐渐以“四书”取代“五经”。而在这过程中,这些理学家,如朱熹等并没有如清人所言般以理代礼,而是认为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即前者是后者的精神内涵。此外,田浩还撰写了《郝经对<五经>、<中庸>和道统的反思》一文。[6]本文虽未直接讨论朱子思想,但它却讨论了学者郝经如何继承和变更朱熹的思想。田浩在该文中指出,在1255年之前,郝经基本上是接受朱熹对于道统的理解的。他虽然对“五经”的看法与朱熹的观点有同有异,但他在后来还是接受了朱熹对于“四书”,特别是《中庸》的观点。但在1255年之后,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郝经改变了过去对于道统的理解。
最后,《<朱子家训>之历史研究》一文则简要地回顾了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世界朱氏联合会有关《朱子家训》研究的发展情况。[7]他将这段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认为《朱子家训》是家庭道德的标准。而到2002年,五位政府官员所发表的论文则显示它是来自封建社会,却依然对社会主义道德标准颇有补益的典型中国价值观。而2010年于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会议中,学者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中国对世界普世价值的重要贡献,应予以推广。
除了田浩以外,以下两位学者亦曾发表论文讨论朱熹的思想。首先,庞安安(Ann A.Pang-White)《朱熹的家庭与妇女观:挑战与机遇》(ZhuXionFamilyandWomen: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一文通过比较朱熹的两类文献考察了朱熹的妇女观。[8]她指出从现实的层面而言,朱熹对于女性的态度是颇有弹性和开明的。其次,朱熹有关阴阳与男女关系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最后,庞教授认为朱熹对于女性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的观点是带有进步性的,并指出这种进步性或源于朱熹形而上思想的稳步发展。
其次,白诗朗(John Berthrong)的论文名为《荀子与朱熹》(XunziandZhuxi)。[9]他撰写这篇论文是为了证明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思路接近荀子而非孟子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及重要性。他在该文中比较了荀子和朱子对于“理”和“心”的理解。白诗朗认为在朱子的体系中,“理”既可作Coherence或PattemmOrder,亦可作Principle。其原因在于,朱子赋予了“理”一个道德内涵。就“心”而言,白诗朗指出朱子对于“心”的理解大致有两点。首先,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或“心妙性情之德”。其次,朱子认为“心”在概念上是单一的,而不是相对的。
另外,在去年10月初,亚洲研究学会美西(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Western Branch)研讨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田浩在会上还主持了一场主题名为“重读朱熹与道学:宋元时期之儒学”的报告会。会议报告者皆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报告的论文题目包括:张晓宇:《转向内在的道:北宋晚期新学派“道学”一词用法之考察》;吴思远:《论朱熹对苏轼的一些看法》;张琎:《大儒之友道:对吕祖谦与朱熹交往的反思》;刘丽丹:《论中韩文化交流中白云洞书院对白鹿洞书院的接受》;温佐廷:《为古道辩护:元好问对道学态度之考察》等等。
就学位论文而言,当中虽无专谈朱熹或朱子学者,然仍有两篇博士论文约略讨论了朱熹的华夷观和他关于“命”的看法。前者为杨劭允(Shao-yunYang)所撰写的《重塑蛮族:中华帝国中期(600—1300)对夷狄在修辞及哲学上的运用》(Reinuentingthe Barbarian:Rhetoricaland Philosophical Uses ooftheYi-Di in Mid-Imperial China,(600-1300))。[10]而后者则是由白英宣(Youngsun Back)所撰写之,《掌握命运:儒家对命的论述》(Handling Fate:TheRu Dis-course on Ming)。[11]杨劭允的论文探讨了唐代至元代学者华夷观的演变。杨劭允在论文的第八章中依次讨论了朱熹等道学家是如何理解华夷之间的区别的。他指出朱熹认为人与夷狄是截然不同的,而只有中国人才算是真正的人。其次,杨劭允指出朱熹并没有明确地通过“理”和“气”的概念来解释人和夷狄的不同。因他的学术旨趣并不在此,而且朱熹也意识到这种做法有一定难度。同时,杨劭允又认为朱熹对于华夷的态度既与其他道学家有异,亦使其道德哲学表现出种族优越的特色。
白英宣的论文以纵向的方式探讨了“命”这个概念的演变。在该文的第二部分中,白英宣比较了朱熹和丁若镛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她首先指出朱熹学说的宗旨是希望人们能实践成为圣人的方法,而她在论证过程中亦提到朱熹认为“天”与“理”的意思是相同的。随后,她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朱熹有关天命、立命和正命的问题。她指出,在朱熹眼中,“命”与“理”和“气”是有关联的。又据她所言,朱熹认为只要人们能实践成为圣人的方法,那么他们便可得到正确的“命”,反之亦然。
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
〔韩〕姜真硕
2014年韩国的朱子学研究大概可区分为五种领域。从研究范围看,分别有关于“四书”或“五经”的朱子注释书的研究,关于朱子学与宋代儒学的研究,宋儒文献或《朱子文集》传播于朝鲜的研究,朝鲜朱子学的话语及其内容之研究,关于李退溪、李栗谷、丁若镛等朝鲜大儒的研究。其中,笔者把值得给读者介绍的论文按照几种研究领域区分如下。
第一,关于“四书”或“五经”的朱子注释书的研究。
Min Hyoung-hee:《<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历史学研究》53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一方面介绍《四书章句集注》给南宋士大夫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朱熹对“五经”和“四书”的见解。作者认为朱熹似乎把“五经”看作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五经”类的文化产物中难以找出基于道统的道德规范。为了帮助学生寻求内心的道德规范,朱熹选择了既更具整合体系又更善于提出他的思想体系的四种文献,即“四书”。为了把文化传统与他的形上学体系成功地结合,朱熹重新定义了儒家的文化伦理传统,并把天地概念注入其中。
Kim Do-il:《在朱子对<大学>的解释中的实践问题——“止于至善”为何是独立的纲领?》,《退溪学报》136卷,2014。
作者强调“止于至善”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完成。换言之,“止于至善”之实现,是道德修养的人从“明明德”出发,扩充为“新民”,在更为扩大的共同体中不断实践后才能完成的。
陈礼淑:《孔子诗经观与其后学的反响——以朱子与其后学为主》,《汉文学论集》39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详细介绍了朱熹对孔子删诗说的看法有时期的区分。早期朱熹相当接受孔子删诗说,承认孔子“去其重复,正其纷乱”的积极角色。之后,因受到彻底不信且批判诗序说的郑樵的影响,朱熹放弃诗序说,修正孔子的删诗说。后期,朱熹进一步认为孔子只言郑声淫乱,而无言删去诗,因此“孔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由此可见,朱熹前期和后期的诗观,有删诗说与刊定说之区分。
第二,朱子学和宋代儒学的研究。
Hong Sung-Min:《在朱子的伦理学中的差等对待的正当性》,《中国学论丛》43卷,2014。
作者在分析朱子“参赞化育”思想的过程中指出朱子以诚之态度把我们的关心和关怀扩大为整个万物之生命,这些学说可成为朱子哲学之生态伦理的理论根据。天地的生命意志与人的伦理实践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由此可找出等同又差等的逻辑之可能性。基于这些内容,我们可确认朱子生命伦理的差等对待是与“各得其所”息息相关的。
Boo Ji-hoon:《张载的大心工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以格物致知为主》,《东洋哲学研究》78卷,2014。
作者认为朱熹对于张载的大心工夫以扩充知识方面始终保留怀疑的态度。如果没有格物穷理的支持,仅仅做大心工夫只不过是空虚地扩充内心。朱熹解释格物致知时强调见闻知,他一方面接受张载提出的见闻知与德性知的两层结构,另一方面弄清此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树立自己的哲学。在朱子哲学里,见闻知被看成外在知识的所得,而德性知被用于内在修养之完成。
Shin Chun-Ho:《德治的目的和难点——关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论争的考察》,《韩国道德教育学会》年次学术大会,2014。
作者说明陈亮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要排斥道和义的道理。他强调的是在实际统治的现实中不能忽视义和利的两面,应该同时考虑此二者才能实现完善的统治。作者进一步认为,陈亮提出周公的统治例子成功地反映了他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由此看来,陈亮认为,朱熹提出的德治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出实际效应,应当依法实行赏罚制度。
第三,宋儒文献或《朱子文集》传播于朝鲜的研究。
Song ll-Gi:《永乐内府刻本<四书大全>的朝鲜传来与流布》,《韩国文献情报学会志》48卷,2014。
作者介绍了明代中国编纂的《四书大全》,世宗一年(1419)首次传播于朝鲜。世宗八年(1426)和世宗十五年(1433)再传至朝鲜。世宗八年(1426),世宗命令庆尚监司刻印《性理大全》《五经大全》。朝鲜时代刊行的《四书大全》集中刊行于庆尚道和京畿道等地区,而且集中刊行于18世纪即壬辰倭乱。清朝顾炎武等学者严厉批判《大全》本的刊行时,朝鲜境内《大全》的刊行反而最热,显示了当时两国学术风气之不同。
Lee Young-Ho:《朝鲜的朱子文集的注释书及其意义》,《大同文化研究》88卷,2014。
作者介绍了朝鲜学者对朱子文献的注释及其演变,认为朝鲜时期最早的注书是对李退溪《朱子书节要》一书当时和后代的注书。宋时烈注释《朱子文集》,完成了《朱子大全箚疑》,宋时烈的弟子们在之后的二百年间进行了修改。经历了这些工作,李恒老等学者终于完成了《朱子大全箚疑辑补》。朝鲜朱子学的朱子学文献的注释面貌可谓从宋时烈的《朱子大全箚疑》出发,到《朱子大全箚疑辑补》完成。
第四,朝鲜朱子学的话语和其内容之研究。
Kim Baeg-hee:《朝鲜前期儒学的伦理主体性的形成与变换——以郑道传和李退溪为主》,《东西哲学研究》74卷,2014。
作者介绍了朝鲜时代的代表人物。郑道传是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李退溪则是在朝鲜中期士祸不停之际重新解释朱子学的儒者。作者认为郑道传构想的伦理主体是奉献于建设共同体的朱子学之人。他们认同社会一体化的理念,是为社会全体做贡献的集体智慧之一员。相对地,在守成期活动的李退溪所构想的伦理主体则是以朱子学的理念为自我认同,把道德价值能动地实现于社会的人。因此李退溪特别强调理发之能动性。
Kwon Oh-young:《朝鲜朱子学的理学话语及其特色》,《朝鲜时代史学报》69卷,2014。
作者认为朝鲜朱子学重视穷理,更重视敬的修养。李退溪建立朝鲜朱子学的体系时,提出敬为核心概念。以退溪学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归结于敬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周世鹏建立白云洞书院时把敬字刻在河上岩石。李退溪继承这些朝鲜的敬传统,又传承真德秀的《心经》传统,提出朝鲜儒学的敬哲学。
Kim Woo-hyung:《金昌协的知觉论与退栗折中论的研究——知觉与智的分离所产生的道德心理学的见解》,《韩国哲学论集》40卷,2014。
金昌协是在朝鲜时代人性、物性同异论争时期活动的儒者。作者从李退溪和李栗谷思想的折中意义上来探讨金昌协的知觉论。金昌协继承了宋时烈重新树立朱子学的时代意识,把退溪学和栗谷学的综合作为自己的时代课题。为了说明这些内容,他试图把心知与智知作为整合的范畴而发挥他的思想。金昌协在心论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宋时烈的思想,而由此进一步发挥知觉是兼心之体用的学说。他的退栗折中论可说是把“理乘”义引申为如李退溪把理发义看成内在于善之本性的道德原理。
第五,朝鲜大儒的研究。
Jeong Sang-bong:《茶山的人们观与孝悌慈的实践》,《韩国哲学论集》43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从伦理学的角度重新探讨丁若镛的哲学思想。作者认为,在丁茶山的思想中,人兼备身体倾向与精神倾向。其中,特别是好善恶恶可说是人的本质,是上帝之天赋予人的。人具有自律的判断能力和具有主体之实践意志的自主之权。人虽然有向善之倾向,但是具有自律又主体特色之人的行为是有善有恶的。上帝随时随地监察人的动机和行为的善恶与否。上帝之声是从人的道心中响彻出来的。这就是伦理实践的外在动因,也是内在动因。
Kim En-zhong:《丁茶山对朱子<论语集注>的批判(七)》,《汉字汉文教育》33卷,2014。
这篇论文是作者关于丁若镛对朱子学的批判方面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介绍了丁若镛否定仁之内心说,而主张人心具有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理发现于外而在行事中实现的是仁义礼智。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归”的解释方面,朱熹说:“归,犹与也。”丁若镛解释“归”为归化义。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解释方面,作者认为朱熹把足食和足兵看成民信的一种先决条件,茶山则认为三者各为一事,不一定互相有关系。在“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解释方面,朱熹比较重视君主与百姓的上下关系,茶山认为君主与百姓皆是以信任为基础,在同等关系上互相作用的。
以上大概介绍了2014年韩国朱子学研究的内容。各领域的研究分别显示朱子学、朱子文献学、朱子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朝鲜朱子学对南宋朱子学的继承和修正、其他朝鲜大儒的哲学等内容及其特色。除了笔者在这里介绍的论文之外,韩国学者每年都认真地研究退溪学、栗谷学、茶山学等韩国儒学的三大领域。不过,在2014年的研究成果中,我们难以找到传承韩国朱子学或解释朝鲜儒学而提出的一些应用哲学或现代伦理学方面的论文。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3—2014年韩国栗谷学研究综述
赵甜甜
韩国对朱子学的传承和发展在儒学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由于朱子学是朝鲜王朝建国的理念,而儒学知识阶层的掌权更是使朱子学在韩国逐渐本土化,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使朱子学不仅仅在理论层面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更深入到实践之中,渗入到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栗谷李珥在朱子理论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韩国朱子学进行研究时,栗谷思想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
此篇综述的数据是基于韩国三大论文检测网站“RISS·KISS·DBpia”上的结果,可能会有不详尽之处,请各位学者大家指正。
2013—2014年关于栗谷思想研究的单行本有24本,其中李光虎所著的《退溪与栗谷,思想的花火》一书,通过分析退溪和栗谷之间往来的书信,找出二人思想的碰撞点,使读者不仅能看到两位韩国大儒的思想花火,还可以体会到学术交流的乐趣。作者李光虎四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学真理,并努力从现代人文学的角度上重新阐释经典,本书有史以来第一次汇编了二位大儒往来的书信及诗文,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二人在学术上各自所坚持的信念。退溪的理论体系非常重视理想世界和人类的内在世界,而栗谷的理论体系则更加重视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外在世界,二人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讨论。读者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二人的思想,更可以从中获得许多人生的智慧。
《儿童击蒙要诀》则以栗谷最著名的《击蒙要诀》为基础,从立志、革旧习、持身、读书、事亲、丧制、祭礼、居家、待人、处世这几个方面,简单明了地向初学入门的孩子们介绍了为什么要学习,如何学习,要学习什么,以及如何为人处事等等。《击蒙要诀》是栗谷为了启蒙儿童和初学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对于学生来说是一本可以受用一生的著作,译者(HAN MUN HI)在忠于原著的同时,以更加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解释方法进行了阐释,对初学儿童的教育极具意义。
《栗谷李珥评传——朝鲜中期最优秀的经国大家·伟大的导师》一书是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永愚的新作,此书从栗谷的家庭入手,对其母亲申师任堂的子女教育进行了肯定,对栗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和思想,并认为栗谷是社会思想改革的先驱,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是不容忽视的。
2013—2014年间有关栗谷思想的学术论文共有77篇,大部分论文是对栗谷思想或栗谷学派思想的研究,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不乏比较研究和跨领域交叉研究。比如金世贞在《율곡학을 통해 본 인간과자연의소통과공생의해법》(《从栗谷学中寻找人与自然交流和共存的解决方案》)一文中,分析了西方生态学的特征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对栗谷学中的生态理论,以及其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寻找出栗谷学中人与自然的交汇点。栗谷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在参与天地化育的过程中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实理以实心的形态内在于人类,通过诚实心可以与实理统一,亦即人类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起到了克制的作用,也将成为人与自然共存与沟通的思想基础。
俞成善则在《中国的栗谷学研究现况及成果研究》中指出栗谷及栗谷学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现阶段对韩国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理学的研究上,其中又以退溪学与栗谷学为主。中国学界对退溪学和栗谷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中韩国际学术会议的开展,与中国国内韩国研究所的合作,对韩国哲学研究的深化和扩大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作者站在东亚思想的角度上,客观地评价了栗谷学研究的意义所在,认为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和栗谷学研究急需培养专门性的人才。
《‘실천학’‘으로서의’실학' 개념 : 율곡 개혁론의 철학적 기초:》(《作为“实践学”的“实学”概念:栗谷改革论的哲学基础》)一文以历史学界在过去80年对“近代实学观”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分析“实学”的概念。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文章从栗谷“实心”的概念出发,对栗谷学中从“实理”到“实心”,从“实心”到“实政”,从“实政”到“实行”的“实心实学”概念进行再解释,认为这种积极强调践行的“实践学”思想植根于栗谷的改革论之中,并形成了茶山丁若镛的“行事”概念和东学的“学”概念。
相比较而言,近两年关于栗谷思想研究的学位论文较少,共计有12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只有2篇,硕士论文10篇。这些硕士论文选题新颖,摆脱了传统思路,试图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解释栗谷思想,如:《퇴계와율곡의 성 리학 사상으로 본공간조형개념 비교 연구》(《退溪和栗谷的性理学思想与空间造型概念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退溪和栗谷的性理学思想在韩国传统建筑的空间造型艺术中有很多体现。例如,天地秩序体系中的谦虚与恭敬思想体现在空间的大小、构成、布局和位阶、秩序上,而建筑正南向的布置,明确的区域功能划分及空间的开放性则是礼思想的体现,建筑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则体现了天地和合的思想。
徐明子在《栗谷의孝思想研究:“圣学辑要”‘孝敬章’을中心으로》(《栗谷孝思想的研究:以<圣学辑要·孝敬章>为中心》)一文中,从“孝敬”入手,分析孝敬的重要性,找出孝敬理气论的根据,认为以孝守身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文中强调这种孝并不是愚孝,而是可以谏言的孝,孝的方法则可以分为“生事之道”“丧礼之道”“祭礼之道”。
《栗谷의 저술에 나타난자녀교육관 연구》(《对栗谷著作中出现的子女教育观的研究》)中以子女教育作为切入点,系统地考察整理了栗谷著述《同居戒辞》《击蒙要诀·事亲章》《击蒙要诀·居家章》《圣学辑要·正家篇》以及《小儿须知》中所体现的子女教育思想,认为其榜样教育、适时习惯化教育、知行并进教育以及理性对话的训诫教育不仅在朝鲜时代,而且对现代的子女教育也十分具有典范作用。
2013—2014年关于栗谷思想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会议莫过于2014年10月31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600周年纪念馆隆重召开的主题为“东亚朱子学与栗谷学的位相”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韩国栗谷学会与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BK21事业团共同主办,同时得到了栗谷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栗谷学会会长崔英辰希望东亚各国都能以“朱子学”为核心,跳出“一国史”的观点,从“东亚史”的层面上寻找各国儒学的同异,摸索出现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来自法国、日本、中国的知名学者以及极具潜力的新晋学者们做了精彩的发言,为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研究和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其中孙兴彻在《栗谷理通气局说的内包和外延》一文中考察了栗谷理通气局说的发展和变化,而李向俊则在《理,事物,事件——李珥的情境》中活用西方最新的分类学学术成果,结合栗谷理气心性论的构造进行探索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在论文集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2013年年底“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的结集出版。“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2012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成功召开,由于此次会议跨越了多个学科、多个领域和多个地区,有27个议题,69个场次,所以其论文集的出版显得难能可贵。收录在《东亚视域中的儒学:传统的诠释》一册中的论文有多篇涉及了栗谷思想,尤其是崔英辰《19—20世纪朝鲜性理学“心即理”与“心即气”的冲突:以艮斋和重斋对寒洲“心即理说”的论辩为中心》一文中,系统整理了退溪和栗谷学派对于心、性、理的看法,而栗谷思想对于后代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影响深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栗谷所编撰的《击蒙要诀》现在仍作为中小学生必读书,其所产生的教育意义在现代社会仍不可估量;而其母亲申师任堂也作为现代社会女性的典范,不断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因此可以说栗谷思想中所承载的孝思想和教育思想至今传承不息。
对于栗谷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韩国国内,中国也开展了相对活泼的研究活动。大陆学者除了陈来、李甦平、潘畅和,还有很多年轻学者,例如邢丽菊、洪军等。而中国台湾对韩国儒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栗谷学方面的专家,在此不一一赘述。
(作者单位:韩国成均馆大学校)
2014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板东洋介林松涛译
1.现代日本思想界关注儒教——《现代思想》儒教专辑
《现代思想》杂志2014年3月期(青土社)推出了一个专辑,题为《当今为何谈儒教?》。日方作者有:安富步、土田健次郎、中岛隆博、石井刚、泽井启一、吾妻重二、井上厚史、伊东贵之、羽根次郎、本间次彦、马场智一(按撰稿排序)。中方作者有:张志强、谭仁岸。此外还收有两篇对谈——当代日本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与文艺评论家、台湾史专家丸川哲史之对谈,以及载于《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清华大学,2010年10月)的齐泽克(S.Zizek)、鲁策(A.Lusso)、海裔、汪晖四人谈的日文译文。代表了当今日本水准的儒教研究者及评论家群英荟萃,蔚为壮观。《现代思想》是一份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思想性杂志。每期“专辑”介绍一些欧美著名的思想家、欧美社会与政治思想、日本国内与国外的时事问题等,其选题反映出日本知识阶层的关心所在之推移,本期《当今为何谈儒教?》这一标题在其中独放异彩。在2014年的日本,《当今为何谈儒教?》——这当然既不是挖掘业已过时、化为“知识化石”的思想,也不是如在博物馆眺望陈列品。无非因为中国大陆对2014年的日本而言,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领域获得了对昔日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影响力,几乎成为最巨大、最重要的“他者”。然而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共同体的决策架构,对外部的人来说还是雾里看花。因而,当今的日本人自然地将强烈的关心投向曾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整合之原理,近年来随处听到“复兴”呼声的思想上与礼制上的传统——儒教。其中存在着希望理解他者的迫切愿望。
本期杂志的撰稿人大半或含蓄或明确地表明了上述及其当下的问题意识,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日本学者共同拥有的态度。例如,谭仁岸与张志强分别介绍了在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叶的中国“传统”儒教的复兴过程,文中仿佛渗透出在传统儒教与近代乃至共产主义之间激烈摇摆的当代中国的热气沸腾(《传统现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儒学の“创造的转化”(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与此相对,日本作者较多作为主题的则是,如何自我反思潜在于以往的日本人的儒教观之下的意识形态。例如,泽井启一批评了以往的日本儒教研究中存在的“仅关心儒教‘日本化’的日本中心主义”倾向,相反将以往被视为儒教“日本化”的现象作为儒教本身内在的“本土化”运动之一环来反思(《土着化儒教日本(本土化的儒教与日本)》)。另外,井上厚史论述了井上哲次郎(1855—1944)与高桥亨(1878—1967)等战前帝国日本的儒教研究之泰斗们如何恣意地制作出停滞的朝鲜儒教与先进的日本儒教之对比构图(《封印朝鲜儒教(被封闭的朝鲜儒教)》)。此外,尤其是对引领了战后儒教研究的沟口雄三(1932—2010)的中国观,也进行了可谓相当严厉的反思(伊东、吾妻、本间论文)。这样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与其说是当今活生生的儒教,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迄今为止对儒教的态度构成了主题。究其缘故,一是由于日本不同于中国大陆,儒教不管是作为思想教说还是礼仪制度都未融入现代日本生活中,另一是由于日本受到了较之活生生的现实,更关心“话语”内部权力性的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互动。当然,往昔日本的儒教观中存在的“落后的大陆、进步的日本”这一价值意识,在当今仍很难说已被彻底根除,不断找出此类狭隘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日本人来讲,仍是当下迫切的问题。可是,“重新谈论儒教至今是如何被谈论的”这一态度,归根结底不得不说是在学术界内部“自我言及”性的,这是与在中国或在韩国一谈起“儒教”便会出现的属于这一社会的人无不关心的热气沸腾所无法比拟的。作者之一中岛隆博一方面关注试图通过复兴读经与释奠等来恢复地域社会之公共性的中国现状,一方面针对因反思战前压抑性的“国民道德”而造成的战后完全空白化的日本地域性公共空间,这样写道:“不妨摸索一种以不同于国民道德及‘教养’的方式来尝试参与公共领域的儒教之可能性。”(《儒教、近代、市民的 (儒教、近代、市民性灵性)》)大约在日本,通过在地域开展礼仪、实践来重塑“地方性、市民性的灵性”(上述中岛论文)真正起步时,作为“传统”来参考的不是儒教,而是佛教与神道,但中国的儒教传统之复兴同时也引出了在现代日本如何构想“家礼”与“乡礼”这一极为现实的问题。
2.山崎暗斋与朱子学的“本土化”——泽井启一《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
正如上节所述,贯穿于当今日本儒教研究背后的倾向变了,整个基调从寻求日本儒教的独自性,转向关注其与东亚儒教文化圈整体的联动性、互动性。这一倾向显著地表现在有关山崎暗斋(1618—1682)的研究、论著之增加上,耐人寻味。战后日本的近世儒教研究中以往最受瞩目的是全盘否定朱子学,树立起独自思想体系的荻生徂徕(1666—1728)。自丸山真男的划时代巨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以来,在徂徕思想中发现了日本独特的先驱性近代,以及日本儒教的独特性与先进性。然而,近年来仅专业性著作就出版了高岛元洋《山崎暗斋——日本朱子学垂加神道(山崎暗斋——日本朱子学与垂加神道)》(ぺりかん社,1992)、朴鸿圭《山崎暗斋の政治理念(山崎暗斋的政治理念)》(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田尻祐一郎《山崎暗斋の世界(山崎暗斋的世界)》(ぺりかん社,2006),今年又有泽井启一《山崎暗斋——天人唯一の妙、神明不思议の道(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ミネルヴァ书房,2014.3),暗斋研究凌驾于徂徕研究之上,呈现出一片欣荣。
近年暗斋研究之盛与暗斋本人在思想史上所占的极其微妙的地位相关。仰慕朱晦庵之名而自号“暗斋”的山崎嘉右卫门敬义在整个日本近世是一位最醇、最敏锐的朱子学者,他还尊信朝鲜大儒李退溪(1501—1570)。暗斋的思想与实践中重“敬”高于一切的想法被认为来自退溪的影响。可是暗斋同时也是一位倾心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试图合朱子学与神道为一体的人物。作为神道家暗斋自称“垂加”,他开辟的垂加神道在近世形成了最大的神道势力,同时对明治时代以后的国粹主义也施以了巨大影响。暗斋究竟是最纯粹的朱子学者,抑或是狂热的神道家、日本主义者?对此泽井启一甚至说:“暗斋的真面目是儒教抑或神道,以及该两者出于什么理由得以并存?”这一设问“或许可说是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最大的谜”。有学者认为,对于暗斋而言,神道是使朱子学根植于日本风土中的无可奈何的韬晦(朴鸿圭上述著作等),也有学者认为相反,对暗斋而言,朱子学只不过是他彻悟神道中蕴藏的日本固有精神的触媒而已(近藤启吾等人)。山崎暗斋这一思想家恰恰立足于赞赏日本之独特性的民族主义与朱子学这一前近代东亚的普遍性思想的分岔路上。研究中心从徂徕向暗斋转移极具象征意义。
作为今年“ミネルヴァ日本评传选”之一册出版的泽井启—《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如上所述明确了暗斋的特殊地位后,不局限于暗斋的思想,而对其出自、学统、门第、交游,乃至从政治、经济至出版状况的当时知识环境广加探讨,与以往的“较之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更关心)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成立的”这一研究趋势相反,勾勒出了“作为个人”的暗斋像。本书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对构成暗斋研究中的“最大的谜”并一直找不到答案的他接受神道问题,不是如以往那样从“日本固有性”这一文脉来把握,而是作为对朱子学重视的实践(“穷理”与“居敬”)进行“本土化”,即“改变为合于自分的时代与地域者”的一个环节来把握。泽井启一认为,暗斋之接受神道只是承继了源自宋代朱子等人的巨大思想潮流的,各地域、各时代的所有人物——如明代的王阳明与李氏朝鲜的实学者们,以及近世日本的古学者们——分别与自己的时代、地域相结合,对实践方法加以修正的尝试之一。泽井启一关注的是在暗斋生活的近世日本社会中儒教式礼制未扎根这一点。在近世日本社会,政府强制规定丧葬以佛教式进行,并且也未开展《小学》中体现的礼法之幼年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能与周围不产生矛盾而履行“敬”之形式,他发现了神道礼仪与实践。泽井启一得出的结论是“用神道这一‘本土’素材”“在日本使朱子学得以实践”才是暗斋根本的目标。这一理解当然是载于《现代思想》的论文《本土化的儒教与日本》中泽井启一本人所提示的见解的具体应用。不拘泥于日本的固有性,从“东亚”规模来把握日本儒学,这正是当今学界所共有的姿态,以这一姿态来具体地探究一位思想家,能够开辟出怎样的新视野?泽井启一的著作如此给出了一个范例。
3.奔波于东亚的朱子学者——《季刊日本思想史》朱舜水专辑
整个近世日本,水户藩(现在的茨城县)一方面作为德川的“御三家”之一,成为德川军事政权之重镇;而另一方面,好学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招请明朝遗臣朱舜水(1600—1682)开设彰考馆之后,也作为日本近世的儒学研究中心延续下来。“水户学”在近世儒学界一直占有独特的位置,直至近世末期,作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性动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参与维新的志士们无人不受“水户学”之影响。维新后,水户学相关资料之大半秘藏于水户德川家,其中包括众多与朱舜水有关的资料。近年来,这些资料移归公益财团法人德川博物馆保管。2010年台湾大学举办“朱舜水与东亚文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契机,2012年开始了为时三年的史料调查。由中、日的研究者参加的该项调查之结果作为《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I——朱舜水文献释解》(2013)、《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Ⅱ——德川光国文献释解》(2014)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东亚各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明年预计出版《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水户藩的内外关系文献释解》。《季刊日本思想史》杂志第81期(2014.9)以“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之学问”为题,向学界公开了目前的部分研究成果。中、日学者基于新资料各自发表了探讨朱舜水及与德川光国相关问题的饶有趣味的论文。其中包括朱舜水来日前的活动、德川光国与朱舜水的相识、光国之思想形成、舜水带来的书画与夫子像之实际内容、安积澹泊(1656—1737)等舜水门弟们的思想,以及实际上如何接受舜水带到水户藩的思想中大约最重要的朱子学式礼法的情况等,弥足珍贵的一册著作让读者联想起以舜水与光国为中心的水户朱子学之概况。
其中受到关注的是,此次证实了以往的舜水研究中对是否实有其物争论不休的舜水所持南明鲁王之敕书,并在该杂志上登了照相版与翻刻。对2013年9月2日“发现”敕书时调查团成员的神情,杨儒宾做了如此描述:“九月二日,传说中的‘鲁王敕书’由博物馆员解开纽解,当我们看到朱舜水生前秘藏而不示与人的那封敕书时,调查团的成员都在静悄悄的馆内或感叹不已,或瞠目结舌,或热泪盈眶。……”(《异乡家乡——鲁王朱舜水の物语(异乡与家乡——鲁王与朱舜水的故事)》)
大约四百年前朱舜水所扬帆渡过的,正是今日化为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冲突之地的中国大陆东方、日本西南方之水域。迢迢万里来到远东之岛国,乃至更东方的水户之地,不改敬奉明之遗王态度的朱舜水之身姿,形象地向年轻有为的君主德川光国显示了对构成朱子学之核心的“理”之无穷的信仰究竟为何物,这促使德川光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当时日本尚且陌生的,作为舶来新思想的朱子学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来到日本之一瞬。据说放置舜水所秘藏的鲁王敕书的木匣,在幕末弘道馆之战中刻下深深的弹痕(德川真木《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关于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弘道馆之战发生在舜水去世一百八十年后的1868年,这是一场学习奉舜水为祖学的水户学的水户藩士们中的保守派为死守水户藩学馆弘道馆,与站在新政府一方的革新派交火,双方死伤惨重,并令弘道馆之大半与珍贵的典籍一同化为灰烬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战争。奔波于东亚的朱子学者舜水、与舜水有关的水户学者们虽然都是为了理而不辞行使武力之人,可是舜水亲身传至日本的朱子学之神髓不是向国外胡乱炫耀暴力等,而是不屈于任何逆于理的权势与暴力的英勇的自立姿态,面对这位对日本道学有大恩大德的先儒,今日仍需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作者单位:日本学术振兴会)
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傅锡洪
朱子学初传日本是在朱子去世后不久的13世纪初期,不过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朱子学文献被淹没在浩瀚的佛教文献当中,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直到17世纪初期,日本结束战国时代,进入比较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江户时代(1603—1868)以后,由原本是僧人的藤原惺窝发其端,朱子学才开始兴盛起来,并且涌现出林罗山、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山崎暗斋、中村惕斋、贝原益轩和新井白石等一大批杰出的朱子学者。朱子学不仅在江户时代前期的日本思想界占据着中心地位,甚至也可以说,当时整个东亚世界朱子学研究的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了日本。
从江户前期到现在又已过去四百年。在这段时间里,朱子学在日本虽然最终并未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其命运甚至也可说几经盛衰沉浮,但对朱子学的研究在日本却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屡有创获。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充分吸收和消化其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今后深入推进朱子学研究所需面对的课题。而当下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在继承原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在发生着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
本文将目光投向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的成果,从中或可窥看当下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某些特色和动向。根据这一年成果的分布情况,本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有关文献考证、经学解释、家礼实践和文化交涉等议题上。
1.种村和史:《严粲诗辑所引朱熹诗说考》
众所周知,朱子《诗经》研究经历过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对小序(相传为子夏所作)的态度:“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朱子语类》卷八十)其最终成果即为今本《诗集传》,该书完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而在此之前的“诗解文字”则已亡佚。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朱氏集传稿”,另外朱子曾说:“《诗传》两本,烦为以新本校旧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朱文公续集》卷八《与叶彦忠书》)其中的“旧本”所指当与前述“诗解文字”和“朱氏集传稿”相同,束景南称之为《诗集解》。旧本中与新本不合者均被朱熹废弃。《诗集解》虽不传,但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1182年朱熹、尤袤序刊)(以下简称《吕记》)、段昌武《毛诗集解》以及严粲的《诗辑》等书保留了《诗集解》的逸文。束景南据上述三书,辑录了《诗集解》逸文。[1]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种村和史的《严粲诗辑所引朱熹诗说考》一文即是对严粲《诗辑》所引朱子诗说的研究。[2]严粲(生卒年不详)[3]撰写了《诗经》注释书《诗辑》(淳祐八年,1248年自序刊本),种村论文的核心是辨别严粲所引朱熹诗说中的新说和旧说。不过种村也指出,他是按照学界通行的做法,将《诗集传》以前,尊重小序阶段的朱熹诗说统统放在《诗集解》的名下加以讨论,因此《诗集解》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具有一定的“假想的性格”。
《吕记》所引朱子之说为旧说,当属无疑。[4]但严粲和段昌武所引则有讨论的必要。种村在第一节“问题设定”的部分介绍了先行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观点。束景南认为段昌武和严粲“二人均为主毛序说诗派,二书亦皆仿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而成……故二书中所引‘朱曰’、‘朱氏曰’,必为朱熹主毛序说之《诗集解》,而非黜毛序说之《诗集传》”[5]。彭维杰则认为:“如较朱子晚出多年之严粲,所著《诗辑》,引朱子说者五百余处,其间有引朱子旧说……亦有引朱子晚年定说者……欲探严氏引朱子旧说、新说,则必先考其引文别其新旧。”彭维杰证明所引为旧说时提供的依据是“吕氏《读诗记》引文同”,而新说的依据是与定本《诗集传》相同,但是“未见吕氏《读诗记》引之”。[6]种村指出,若按彭维杰之说,则束景南的《辑录》中混杂了朱子的新说,与此同时,彭维杰之说也存在问题:“吕祖谦在朱子的诗说中选择于自己有用的部分加以引用,其所引用的并非朱子旧说的全部。因此不能仅因不见于《吕记》便断定其为朱子的新说。”[7]严粲所引朱熹诗说,若要确定为新说的话,需要满足如下的条件:《吕记》在相应的地方不仅没有引用这一说法,反而引用了与此说完全不同的朱熹的另一说法。这一看法构成了种村全文论述的一大支柱。
在第二节“比较的方法和判别的基准”部分,种村在理论上将严粲所引朱子诗说的来源分为四类:1.转引自《吕记》;2.引自《诗集传》;3.引自《诗集解》本身;4.引用来源不明。他将严粲所引朱子诗说共计589例与《吕记》所引朱子诗说、朱子《诗集传》进行对比,指出实际存在的五种情况,并制成如下表格:
种村总结道:“在旧说与新说不同的前提下,2.1、2.2和4,严粲所据为旧说;3.2所据则为新说。这也表明,站在尊序立场上的严粲,将持反序姿态的《诗集传》作为参考资料而加以使用。”[8]而589例引文具体情况则附于文末附表《〈诗辑〉所引朱熹诗说一览》中。
种村在第三节“三书关系的实例”中举出实例,第四节从“《诗辑》所引朱熹诗说的多样性”“《诗辑》所引《诗集解》逸文的数量”“严粲对朱熹新说的接受”“严粲对朱熹诗说的重视”“朱熹诗学的影响力”和“《诗辑》所引朱熹说的校勘价值”六个方面概括了“考察所得以了解的事项”。如第五项,种村指出,朱熹对后世学者而言是具有多样性的巨大存在:“不仅是否定了诗序,在《诗集传》中以自己的思想重读《诗经》的朱熹,而且是他自身决意废弃的,基于诗序的《诗经》注释,也同样持续地强烈影响着后世的学者。”[9]
第五节,种村探讨了严粲得到《诗集解》的途径。种村质疑了束景南《诗集解》曾刊刻流传的观点,认为其只是以手稿形式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流传。至于该书如何传到严粲手上,因为史料不足,目前无法推断。第六节,种村简单介绍了遗留的课题和未来的研究计划。总体而言,全文材料充实,论述清晰,观点鲜明,可以说不仅对先行研究进行了修正和深化,而且尽可能地对《诗辑》所引朱子诗说的时期逐一进行了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材料。
2.鹤成久章:《关于<四书纂疏>所引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
南宋末期赵顺孙(1215—1277)所撰《四书纂疏》26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所引朱子之说均注明出自何书,如“语录曰”“文集曰”“易本义曰”等(明代永乐朝编纂的《四书大全》亦引用了《纂疏》但却隐去出典,径改为“朱子曰”);其引自《语录》者亦有不见于今本《朱子语类》或与其文字不同的;保留了不少朱子后学中已散佚文献的逸文。在关注到这些事实的基础上,鹤成久章《关于<四书纂疏>所引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10]一文,以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朱子语录》为核心进行了考察。
鹤成在第一节主要考察了《四书纂疏》的成书年代。从为其作序的洪天锡去世于咸淳三年(1267),可推断该书写成于1267年之前。而在全书出版之前,牟子才为《中庸纂疏》所作序文写成于宝祐四年(1256),且该序提到了《大学章句疏》(即《大学纂疏》),因此《大学纂疏》和《中庸纂疏》应于1256年前后完成。从内容可看出,洪天锡的序是为《论语纂疏》和《孟子纂疏》而写,且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二所收应俊的序,可知《大学纂疏》和《中庸纂疏》率先完成并出版,等《论语纂疏》和《孟子纂疏》完成之后又合并出版。[11]
鹤成在第二节考察了《四书纂疏》所收朱熹及其后学13人文献的情况。如陈淳的《大学口义》《中庸口义》和《语录》已经散佚,但《四书纂疏》保留了大量应是其逸文的资料。鹤成最后总结认为:“朱熹以外的学者的著作被引用之际虽并未明示书名,但《四书纂疏引用总目》所举之书很多已散佚,若将这些引文掇拾整理的话,应是研究朱熹后学‘四书’注释以至整个思想的有益资料。”[12]
第三节,鹤成考察了《四书纂疏》与元明各种‘四书’注释集成类著作之间的关系,指出《四书集注大全》所收朱子及其后学13家的引文很多可以追溯至《四书纂疏》。[13]他在一个注释中还举例道:“《四书集注大全》中源自《四书纂疏》的引文相当之多。略举一例,通常《四书集注大全》引黄榦之著作或语录时称‘勉斋黄氏曰’,引陈淳之著作或语录时称‘北溪陈氏曰’,如果仅称‘黄氏曰’或‘陈氏曰’,则其引文的来源当是《四书纂疏》。”[14]
第四节,鹤成考察了《四书纂疏》所引《朱子语录》的资料价值。今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大全》成书于咸淳六年(1270),《大学纂疏》《中庸纂疏》成书于1256年左右,其时赵顺孙当没有看到《语类大全》,显然使用的是其他《语录》或《语类》。《论语纂疏》和《孟子纂疏》成书于1267年前,赵顺孙也应该未看到《语类大全》。至于赵顺孙参考了何种《语录》,从其《大学纂疏》“读大学章句纲领”“大学章句序”(《中庸纂疏》同)以及《论语纂疏》《孟子纂疏》“读论孟集注纲领”“读论语孟子法”来看,很可能是沿袭了始于黄士毅的语录分类形式,如此则赵顺孙至少看到过《蜀类》或《徽类》。鹤成还分析了一些见于今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大全》和不见于今本,可能源自赵顺孙所看到的古本《朱子语录》的引文,他也指出这些引文不少是断片,有些可能仅是门人提问语而非朱子的答语。[15]
第五节,鹤成指出了数量在2000条以上的《四书纂疏》所引朱子的语录(当然很多是极短的断片式语句)的一些特征。如在黎靖德《语类大全》中以小字形式出现的引文,在《四书纂疏》中大量存在;《语类大全》记载两人所录的语录,在《四书纂疏》中有整合为一条语录的情况;《语类大全》所载一条语录,在《四书纂疏》中有分多处出现的情况;对于陈淳和徐寓所录,《语类大全》多采陈淳录,而《四书纂疏》则用徐㝢录;虽为“语录曰”,但却见于今本《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书(知旧门人问答)的情况也存在。[16]
除了上述分析以外,鹤成论文还详细列举了记载赵顺孙生平资料的文献、《四书纂疏》的各种版本、《四书纂疏》所引朱子后学13家著作的存佚情况以及日本学界研究《朱子语录》的各种文献,若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话,该文乃是有益的参考。另外顺便一提,作为其参考资料之一的佐野公治《<四书>学史的研究》也于2014年年底出版了中文本(张文朝、庄兵译,林庆彰校订,台湾万卷楼图书出版,2014年11月)。
3.福谷彬:《关于<资治通鉴纲目>与朱子的春秋学:以义例说与直书的笔法为中心》
关于《春秋》这一经典为何而作以及如何作成的问题,朱子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语类》卷八十三)朱子认为《春秋》是孔子依据未修之鲁史《春秋》而作,其手法为“直书”:“《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同上)既为“直书”,故朱子一方面认为古文经学记事之凡例、变例之说多不可信:“《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同上)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今文经学寓褒贬于一二字之间的议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同上)而被问及“《春秋》当如何看”这一问题时,朱子的回答也显得非常干脆:“只如看史样看。”(同上)
朱子并未如《诗集传》一样留下《春秋》的注释,但他及其弟子赵师渊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却与《春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其“纲目”的结构设置与《左传》的“经传”颇为一致;另一方面,在“纲”的部分朱子也用了《春秋》的笔法,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例和笔法做了修正。故《纲目》亦可称为朱子《春秋》学的代表性成果。
不过,朱子上述“义例说的否定”和“直书笔法的肯定”的立场,与其在《纲目》中采用的褒贬笔法以及数量庞大的《凡例》之间,却不免存在着隔阂。这正是福谷彬《关于<资治通鉴纲目>与朱子的春秋学:以义例说与直书的笔法为中心》[17]一文的问题意识所在。[18]而他的思路在于:设置“义例说与直书说的再检讨”和“《纲目》凡例与朱子的春秋学说”两节,在分别考察朱子《春秋》学解释的立场和《纲目》所运用笔法的基础上,将这两者调和,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一贯性。
不过,福谷所设定的核心问题是:朱子否定今文经学作为“褒贬”的解读方法的“义例”与其在《纲目》中所使用的“褒贬”笔法及其《凡例》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并未涉及上文提到的朱子对古文经学“传例”的怀疑。相反,福谷在第一节中,恰恰强调了朱子对于这些“传例”有所继承的另一面。福谷指出朱子曾述及西晋杜预之语“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并认为其所指的内容不外乎就是杜预《春秋序》说的“凡例”。“凡例”又称“正例”,是孔子作《春秋》之前已经存在的“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倘若孔子所修《春秋》经文并未按照这些“正例”书写,则称之为“变例”。而朱子对“变例”持否定态度。关于这一点,福谷引用了如下一段话:“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语类》卷八十三)福谷由此指出:“朱子否定存在‘变例’的同时,却也肯定了孔子在《春秋》中有表示褒贬的意思本身。
这也意味着,朱子虽然否定‘一字褒贬’的存在,但认为孔子有着借直书历史以表示褒贬的意图。”[19]
福谷对“义例说的否定”这一全文基本前提的含义进行了厘清:“朱子否定《春秋》的义例说,其所否定的是与‘正例’不同的‘变例’,但对于孔子笔削以前即已存在的‘凡例’的存在却持认可的态度。”[20]不过应指出的是,杜预所概括的凡例,是否均为孔子以前所存在,抑或有孔子所创设的部分,实已难以断定。朱子认为可疑的也不仅限于“变例”而已,且杜预所说的“变例”也并非公羊学的“一字褒贬”。故将朱子之说概括为“义例说的否定”显得过于宽泛,而收束到“变例说的反对”则似又过于狭隘和偏颇。
福谷还引用《文集》卷六十《答潘子善》中如下一段话,以揭示朱子对《春秋》成书过程认识的最终“定论”:“某谓《春秋》为圣人褒贬之书,其说旧矣,然圣人岂损其实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书之耳……或以为若是则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圣人而后作哉?曰:《春秋》即《鲁史》之旧名,非孔子之创为此经也。使史笔之传举不失其实,圣人亦何必以是为己任?惟官失其守,而策书记注多违旧章,故圣人即史法之旧例,以直书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实耳。初未尝有意于褒之贬之也。”[21]须指出的是,本段引文非朱子之语而为潘子善之语。潘子善此说不能成立实属显然。如其所说,则孔子之《春秋》仅为一不失其实之“史”而已,又何足为“经”?而孔子之功又岂在纠正历史记录之失实哉?其答语显然不足以回应或人“何待圣人而后作”的提问。《鲁史》旧名为《春秋》,孔子之所修仍名为《春秋》,但这又何妨圣人置褒贬于其间而别为一经?故其说又何能驳“《春秋》为圣人褒贬之书”?
在前文有关“变例”的引文中,朱子明确说“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朱子亦不得不承认圣人有意褒贬,准此则其“直书说”实不能成立。“‘……《春秋》只是旧史录在这里。’蔡云:‘如先生做《通鉴纲目》,是有意?是无意?须是有去取。如《春秋》,圣人岂无意?’曰:‘圣人虽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为之说不得。’”(《语类》卷一百二十五)朱子此说只能说明不当妄说,而并非证明圣人乃是无意之直书。故正如蔡季通之说,朱子因《资治通鉴》而作《纲目》和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均是有意褒贬,两者本相互贯通,没有矛盾。唯朱子所倡无意之“直书说”则未免与其“有意褒贬”的主张和做法有所矛盾而已。
4.新田元规:《程颐、朱熹祖先祭祀方案中身份的含意——以元明人的评价为线索》
朱子作《家礼》,以此为代表的宋代礼制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杨志刚在其《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将此变革称为“礼下庶人”[22],吾妻重二在《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以<家礼>为中心》一文中将这一变化称为“仪礼的开放”,认为其与朱子学“圣人可学而至”这样的观念有关,并着重强调了家礼对于士庶各阶层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23]新田元规的《程颐、朱熹祖先祭祀方案中身份的含意——以元明人的评价为线索》一文[24]则强调了与之不同的另一面,即对于士大夫而言显示身份的特殊含意。
新田认为:“‘以万民具有成就道德的可能性为前提’的普遍的性格,与‘重视以地位、道德和教养为基准的身份’的差异的性格,原本在儒教的理论中就带有矛盾意味地共存着,在宋人的道德论和礼说中,这两方面的纠葛也并未消解而依然存在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本文极力要注目于在宋人的祭祀构想中,其设想的实践主体是连庶人也包含在内的所有身份的人,还是最多仅限于士大夫这一微妙的差异。”[25]这一视角受到著名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揭示的“以身份显示为目的的仪礼实践”这一问题的启发。伊佩霞指出,家礼实践不仅为了陶冶道德,也是为了防止重新掉入无教养阶层,士大夫期望家礼具备显示社会地位差异的功能。而这一身份区别的含意未必一定被宋人清晰地意识到或者说出来。伊佩霞认为中国整个传统社会中礼制担负身份区分的功能,新田认为以此为基础,至少可以推测在宋人的礼说中,包含着“覆盖庶人的教育”和“士大夫身份的表示”这样的多义性。而身份的含意即祠堂祭祀是士大夫阶层特权性的象征这一点,被元明时代朱子的后继者们明确论述出来。新田本文的目的正是要以元明时期的礼说为线索,将内在于宋人祖先祭祀说中身份的含意予以揭示出来。[26]而本文所选取的原始文献则是元末至明代《祠堂记》一类的文献。
全文分三节,第一节,新田确认了元明人认为宋人祖先祭祀方案的划时代性在于其士庶通用的一律性,探究了他们是如何论证轻视身份差别的祭祀方式的正当性的。第二节,指出关于身份的一律性的优点究竟为何存在着普遍性(万民的教化)和特殊性(适应于流动性社会中的士大夫)这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三节,具体分析上述主张特殊性的观点,指出与其教养论中存在的两面性相对应,宋人祖先祭祀方案中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普遍性和实质上的特殊性这两面。而与道德教养论领域里明学的展开并行的是在祖先祭祀领域里,通过简略化与习俗更进一步妥协,从而将“教民报本”这一普遍性加以实质化的推进。[27]
在行文中,新田引述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如第二节所讨论的是舍弃身份条件的意义究竟是在“包含所有身份”还是“应对流动化”。新田的引用中就包含了明代著名学者丘濬在《家礼仪节序》和另一篇祠堂记中的侧重点并不相同的说法。丘濬在《家礼仪节序》中强调:“汉魏以来,王朝郡国之礼,虽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则荡然无余矣……文公先生因温公《书仪》,参以程张二家之说,而为《家礼》一书,实万世人家通行之典也……夫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世之学儒者,徒知读书而不知执礼。而吾礼之柄遂为异教所窃弄而不自觉。自吾失吾礼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间,阴窃吾丧祭之土苴,以为追荐祷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经术者,亦且甘心随其步趋,遵其约束,而不以为非。无怪乎举世之人,靡然从之,安以为常也。”新田指出丘濬在此强调的是:“在仪礼领域里应当抑制异端的侵蚀,朱熹制定了包含所有身份的人的礼制,力图重建礼的秩序。”即通过适当简化礼仪,使大众均能得到“教民报本反始”这样的教导。而丘濬自身的《家礼仪节》就是在简化的方向上将仪礼加以改订,而谋求“万世人家通行之典”的实质化。[28]
不过新田随即指出:“可是,同样是丘濬,对于朱熹《家礼》的特征‘身份的一律性’,却显示了与《家礼仪节序》重点不同的另一认识。丘濬在祠堂记中,不提‘教民以正确的祖先祭祀方法’‘在仪礼上排除异端的影响’这样的论点,如下文所看到的那样,设定了‘构想能够应对身份的不安定化的祭祀方式’的课题,论述了祠堂祭祀说的意义。”[29]新田接着引述了丘濬的如下一段话:“古人庙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数,上下咸有定制。粤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无土,是故父为士而子或为大夫,父为大夫而子或为士,庙数不可为定制。且又仕止不常,迁徙无定,而庙祀不能有常所。汉魏以来,知经好礼之士,如晋荀氏、贺氏,唐杜氏、孟氏,宋韩氏、宋氏,或言于公朝,或创于私家。然议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变;或为之于独,而不能同之于众;或仅卒其身,而不能贻于后。此无他,泥于古,便于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马氏,始以意创为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创之主,定为祠堂之制,着于《家礼》通礼之首,盖通上下以为制也。”[30]实际上新田全篇论述的一大核心论据,正是来自丘濬的这一段引文。把握了这一点,新田全篇的论旨也就一目了然,无须赘言。
5.吾妻重二:《東儒教文化交涉:觉書》和《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
吾妻重二《东亚的儒教与文化交涉(笔记)》一文[31]从“文化交涉学”的视点出发,勾勒了东亚儒学和东亚朱子学的多个侧面,反映了近年学界悄然兴起的“文化交涉学”研究的新动向。至于作者所说的“东亚”,则指的是中国、韩国、朝鲜、越南和日本这一在古代就有广泛交流的,可称之为“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的地区。并且作者论述的并非儒教整体,而主要是近世的儒教,其中的核心无疑就是朱子学的兴起和展开。“近世”指的是近代以前具有一定的社会体制且维持较长时间的时代。就中国而言,近世自10世纪宋代以降,韩国则是朝鲜王朝后期(17世纪以降),越南是黎朝(15世纪)以降,琉球则是萨摩入侵以后(17世纪),以及日本的江户时代(17世纪以降)。
吾妻在第一节“儒教史的研究与儒教通史”中回顾了以往将儒教置于亚洲或者东亚视域中进行研究的一些尝试或者提议。他提到了1990年6月岩波书店《思想》杂志《儒教与亚洲社会》特集,以沟口雄三为核心的当时第一线的研究者对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儒教各个方面的研究。吾妻称自己当时并没有充分应对“亚洲”这样大范围的准备,同时也因为这些论文多是个别研究而没有加以一般化,即使读了也只是处于消化不良的状况。不过24年这样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以后再回头来看,发现所收的论说相当有趣。不仅论文如此,今井昭夫等人编的《儒教关系史年表》和渡边浩《东亚儒学关联事项对照表——19世纪前半期》等也以其对于事实的简洁介绍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具有给人启发的作用。[32]而在户川芳郎、蜂屋邦夫和沟口雄三执笔完成并由山川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儒教史》中,虽然所讲述的仅仅是中国的儒教,但是却未冠以“中国儒教史”之名,将中国与儒教直接等同,而未考虑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也有儒教。吾妻也由此推测其时沟口或尚未有关于东亚儒教史的构想。
吾妻还回顾了较早提出有必要进行东亚儒教研究的岛田虔次。他在1967年出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后记中说道:“像基督教史多是在泛欧洲视野下写成的一样,儒教史、朱子学史也应首先作为贯通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通史来写……写出将这些方面都合法正当地纳入视野范围内的儒教史、朱子学史,才是当前的急务。”[33]不过遗憾的是,岛田生前并未完成这一设想。吾妻还提到了切入东亚儒学研究的一位前辈学者三浦国雄,其在《朱熹》(人类知识的遗产系列丛书,讲谈社,1979年)一书的终章以“对后世的影响——朝鲜朱子学的展开”为题,对朝鲜朱子学进行了素描。现在看来其论述虽并不充分,但其可贵的尝试在那个时间点的其他著作中却是看不到的。
吾妻指出:“讽刺的是,以前由于研究滞后,撰写通史的材料不足;而今由于个别研究大大推进,资料过度膨胀得写不了通史。”不过,作者认为:“撰写那样的通史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而且也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一方面,由各国儒教研究者分担执笔拼凑而成的并不足以称之为通史;另一方面,应该在怎样的构想下进行撰写,笔者也尚处于犹豫的阶段。从‘以儒教为中心的知的世界’这样说起来则无限广阔的前提出发,对于当前已被研究的人物、著作和思想的特色这样基本的事实的叙述,以及相关的书志学的把握本身,应当都是必要的。”[34]
在第二节“关于‘文化交涉’”中,吾妻首先介绍了与东亚儒教研究有关的研究动向,尤其是作为其起点的三个大型研究计划。第一,2005—2009年由小岛毅领衔的文部省特定领域研究“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跨学科的创作”(简称“宁波”)、2005年创设,由黄俊杰领衔的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以及2007—2011由陶德民领衔的关西大学文部省G-COE“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吾妻自身即是第三个计划的成员。其相关机构设施有国际性学会“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的事务局、关西大学新创设研究生院东亚文化研究科及其纪要《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和研究生论集《文化交涉》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论文集,其中不少涉及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和展开。[35]这三大计划已经和正在推出的成果以及这一领域的其他成果一起,为继续开展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吾妻接着阐述了“文化交涉”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有关“文化”的定义往往只是突出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的,或者只是在静态中把握文化。吾妻则指出,文化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不断流动的。并且基于“文化是通过交涉而形成,而并非原本就固定在那里的”这一基本事实,主张在考察文化时,从“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视点,尤其是与其他地域的接触和交涉的视点来看。这样的研究其实就是要探明,异文化是如何通过接触而被理解、接受,产生影响或最终被加以改造的。[36]
在第三节,吾妻就自身近期关注的几项具体议题——“朱子学的传播与变容”“朱子学的普遍性”“关于周敦颐”“书院、私塾”和“《家礼》的冠昏丧祭仪礼”介绍了“近世东亚儒教的诸相”。作者将其中部分内容融入进《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中,并作为2014年3月15日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朱子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公开发表。[37]其有关朱子学在韩国、越南和日本传播的介绍简洁扼要,无论是想要进入这一领域做深入的研究,还是仅限于浅尝辄止式地了解,都极具参考价值。
在结语部分,吾妻强调:“在谈及东亚的儒教之际,文化交涉的方法以及视点是非常有用的。”接着文章归结到这样一点上:“这样来看的时候,也让人注意到将儒教视作文化来看待这一点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思想的儒教’,不如说是‘作为文化的儒教’当然不能忘了作为思想的儒教,考察儒教具有的理论和哲学是必要的,不过这样的看法过于强烈的话,有关的文化事象就有可能会被忽视。……过去在这一区域里,共享了超越地域和时代的儒教文化,我们也有必要在广阔的视野中揭示其样态。”[38]当然,这样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朱子学。正如吾妻所说:“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39]
吾妻曾长期专注于中国朱子学、宋代思想和仪礼的研究,现在身体力行“文化交涉学”的理念,不仅将视野拓展到日本,而且也几乎是从头开始学习韩国和越南的儒教,全身心投入名副其实的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儒教”研究之中,其求知欲、魄力和毅力之强均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6.其他成果概述
以下快速扫描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的其他成果。
儿玉宪明《朱熹律吕新书序注解》[40]是对朱熹《律吕新书序》所做的校勘、日译和注释。关于蔡元定所著《律吕新书》作者已刊行有关的注解、序文和《律吕新书》原文都采用《性理大全书》所收本。该文是属于文献的基础研究。而有关朱子学乐律方面的研究应该说也尚不充分,有待学界今后推出更多相关成果。
现代汉语中,作为不定冠词标识的数量词被置于名词之前,为了揭示这一标识形成的过程,木津祐子在《作为不定冠词的“一个”的成立前史——<朱子语类>的场合》一文中以《朱子语类》为对象进行了分析。她发现:“‘数量词+名词’这一形式尚未具有不定冠词的功能,而且,名词‘人’和量词‘个’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前面的数词仅限于‘一’;这与将‘一个’置于抽象名词之前是类似的;而且当‘一个’被置于除了‘人’字以外其他表示‘人’的意思的词之前时,这个词之前通常还带有修饰语,即‘一个’与修饰语具有容易共起的关系。在《朱子语类》中,‘个’并非是用于计算‘人’之数的量词,其主要的功能是在文脉中突出名词所具有的属性。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这种文脉所要求的属性与‘一个’共起的现象,与数量词作为不定冠词的标识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41]
中嵨谅《陈亮与陆九渊——朱熹论敌的思想》一书[42]目录如下,序章《先行研究与笔者的立场》;第一部《陆九渊》:第一章《陆九渊思想中的自立与他者的修养》,第二章《陆九渊思想中的讲学与读书》,第三章《陆九渊的春秋学——以与其高第杨简的对比为线索》;第二部《关于<象山先生文集>的诸本》;第三部《陈亮》:第一章《陈亮的政治批判——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书>再读》,第二章《陈亮对历代为政者的评价》,第三章《从陈傅良来看朱陈论争》;终章《陆九渊与陈亮:其出发点的共同性》。[43]
在朱子学文献的翻译方面,2014年亦有可观之处。除了大规模推进的《朱子语类》(以及《文集》)翻译以外,另有两部朱子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土田健次郎翻译的《论语集注》共四册,从2013年出版第一册开始,2014年先后出版两册,至2015年春出版第四册,至此全部出齐。[44]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在翻译和注释朱子《论语集注》之外,还以“补说”的形式引用了日本江户时代与朱子学立场相左的“古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论语古义》和荻生徂徕(1666—1728)《论语征》的观点。这样做的确有助于读者理解朱子注释的独特之处。[45]另外细谷惠志翻译的《朱子家礼》也于2014年出版。[46]
总结和展望
与前几年似乎“沉寂”的现象不同,可以说今年日本学界在延续原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极探索新的突破口。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这一年日本学者朱子学研究的某些特点。
第一,注重文献的基础研究。对中国学界来说,日本学者向来以擅长考证功夫著称,这一点在2014年的研究中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文献的基础研究将为思想研究提供适当的材料,思想研究也唯有在恰当地把握和运用材料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今年的众多著述中,种村和史、鹤成久章、儿玉宪明的三篇大致可归入文献考证类作品自不必说,其他研究也贯穿着对于文献材料的搜集和考察,如新田元规发掘和运用元明时期“祠堂记”这类看似只对历史研究有价值而向来极少受思想研究者注意的文献,而在思想研究上收获宝贵的结论,就堪称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另外,从词汇学、语法学的角度研究《朱子语类》的方法,近来在中国学界似乎相当盛行,日本学界如老一辈的元曲研究专家田中谦二也曾将《朱子语类》作为“语料”进行研究,并进而转入朱门弟子师事年代的考察,而大有创获。对于以思想分析为主的传统思路而言,这一语言学研究的进路或许也能发挥让人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第二,重视朱子的经学思想。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的重心无疑是朱子经学的研究。例如,种村和史涉及了朱子《诗经》注释的发展变化,福谷彬论及朱子的春秋学,鹤成久章有关《四书纂疏》引文的考察,都触及了朱子的经学文献。另外,有关礼乐的文章也包含了朱子的经学思想。有关朱子经学的研究,将是朱子学研究有待深入推进的重要课题,日本学界的这些成果也将给我们提供有益参考。
第三,关注礼乐实践的层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传统以“理气心性”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研究取向,2014年日本学界对于“形而下”的具体实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正如吾妻重二指出的那样,朱子学具有一个文化体系所包含的广度。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哲学思想的朱子学,但是近来对于朱子学在实际生活层面的影响越发关注。2014年不仅有多篇论文关注了礼乐实践层面的问题,而且《朱子家礼》也被翻译成现代日语。新田元规关注了程朱理学祭祀礼仪中的身份等级问题,儿玉宪明更是将视角转向中国主流哲学界很少关注的《律吕新书》和朱子学的乐律、音乐思想。吾妻重二则在东亚儒学的领域中谈论了朱子家礼的传播。实际上,在异域如何具体实行中国传来的礼乐,是困扰这些学者的重大问题,而且能否付诸操作的问题还会影响他们对朱子学的理解和信任。从理论上来说,礼乐能否实践的问题,也牵涉到朱子学或者儒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如何与各地域的特殊性结合的问题。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更对东亚世界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构建文化交涉的视野。朱子学不仅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而且对东亚世界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拓宽朱子学研究的视野,不仅应当像鹤成久章、新田元规一样,将朱子学置于宋元明清这一纵向连续的历史演变中加以考察,而且也应当如土田健次郎一样,在研究朱子学之际,能够横向扩展,关注诸如仁斋学、徂徕学等中国以外地区的朱子学注释和研究。正如吾妻重二所提倡的“文化交涉学”的视野和思路,我们应该积极关注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地的朱子学,充分把握朱子学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文化交涉学的视野和方法正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这种丰富内涵和多元特色。而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实际上也正是朱子学所蕴含的普遍性的具体体现。从江户初期藤原惺窝等人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朱子学具有普遍性这一特点。他们不仅对朱子学倡导的普遍性观念进行思考和体认,并且也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吾妻介绍的三大计划以外,自2013年起,中国大陆也首次以“国家项目”的形式推动日韩朱子学的研究,这也预示着东亚朱子学或东亚儒学的研究将在未来获得更深入的推进,同时也为中国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推进甚至再次成为朱子学的中心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构筑起新的研究平台。种村和史和鹤成久章的文献研究不仅展示了日本学者扎实严密的文献考证功夫,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于基础性文献研究的耐心和毅力,也颇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研究,还为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做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平台,指示了方向。如借助于种村的研究,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1.将其方法运用于对段昌武《毛诗集解》的研究;2.从严粲对旧说、新说的取舍看严粲《诗经》学研究的特色;3.就朱子旧说、新说的差异,探讨朱熹《诗经》学形成发展的过程;4.朱子《诗经》著述的版本、流通与影响。而对于鹤成所梳理的朱子及其后学的文献,我们不仅可以从文献的角度继续对其加以深入系统的分类和整理,而且也可将其运用于对朱子及其后学的思想研究中。而且《四书纂疏》本身对早期《朱子语录》形成史和朱子后学思想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显然也还有待我们加以充分发挥。而吾妻重二所揭示的“文化交涉”的视野和方法,实际上也对朱子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总之,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新的研究的“生长点”,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做法。
第六,充分利用中国学界的成果。放在整个战后70年日本中国学研究史的视域中来看的话,近年来的这一特点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47]较早的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等自不必说,前几年朱杰人领衔出版的《朱子全书》(2010年修订版)等也都成为日本学者使用的必备参考资料。[48]当然对中国学者的成果,日本学者虽也有所辨析甚至批评,但其问题关注点却往往也与中国学者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有一致之处。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学者在研究和出版领域的成果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或认可,在朱子学研究的领域里中日学界的互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趋势也相当明显;但另一方面也督促我们更加积极地吸收日本学界的已有成果和关注其最新动态,在互动中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业绩。《朱子学年鉴》设置“当年各国各地区朱子学研究综述”这一栏目,其目的也无非是加快互动的频率,促进研究成果的传播。
本文在涉及作者问题意识或文献考证等处“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其意图也无非是希望不仅能概括介绍其成果及思路,更能引起读者阅读原文或者就相关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兴趣。至于这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虽也多有评论,但其是非得失,最终也仍有待读者的评判。
(附记:本文写作于撰写博士论文的紧张阶段,写作中恐未必能充分领会作者的原意以及深入准确分析所涉的各个问题,亦请读者与作者见谅,而文责在我则属无疑。另外,王玉、廖明飞、陈佑真、胡珍子等同学帮助复印了许多资料,在此也对其深表谢意!)
郭雨颖
综观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有关朱子学研究及其出版的情形,朱熹(1130—1200)思想体系以及朱子学等相关研究仍然十分丰赡,这些研究或从经学、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的领域、视角来探讨朱子本身的关怀,甚或是研究朱子学的发展。此外,还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台湾学界在近十多年来有关朱子学研究的课题,亦开展出新的视野,这种研究视野主要是以“东亚”作为一个考察儒学的视角,尤其又聚焦在对“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的关注上,由此更为深化,并且更加充实了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因此,以“东亚”的脉络来重新检视儒学,乃至于朱子学论题的研讨会、演讲,甚至于课程的讲授等,亦多有所见。
据初步调查,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对朱子思想或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的统计,专书计有3本,期刊论文有44篇,专书论文有6篇,学位(硕、博士)论文共有15篇,会议论文47篇,更有十余次的专题演讲主题以朱子思想及朱子学者作为关键词。(详细资料请参考“2014年台湾地区朱子学研究相关资料”)以下就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
一、学术会议及演讲
先就学术会议做一简述。本年度举办以儒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共计有四场,其中即有一场是专门以朱子学为研究课题的国际研讨会,依举办的时间顺序,胪列于下:
(1)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台湾朱子研究协会、台湾中文学会、中华朱子学会主办,“朱子哲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14年3月14—15日。[1]
(2)台湾师范大学东亚文化与汉学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跨文化视域下的儒家伦常:政道与治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2014年9月26—27日。
(3)“中央大学”中文系、“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宋明清儒学的类型与流变”学术研讨会,桃园:“中央大学”文学院,2014年10月30—31日。
(4)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儒家思想与儒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南:成功大学文学院,2014年11月21日。
在上述的会议当中,即多可见针对朱子学、“四书”学等相关领域,乃至于海外朱子学等主题的论文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亦于同年出版,刊载于各大学术期刊。
其次,诸多针对朱子学的演讲亦采取新的视角来加以阐说,如关西大学的吾妻重二教授即以《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为题来提出他的观察,吾妻氏认为朱子学所揭示的重点在“格物致知”,即所谓重视“理智”,是一个爱“知”的综合性学问体系。然就现今学术研究而言,对朱子学这一综合性学问体系则多聚焦在形上层面的哲学、思想领域,但吾妻氏认为这样并不足以撑开这一名为综合性的学问体系,他说:
迄今为止,朱子学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领域,也就是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哲学侧面的分析。当然,朱熹的学问具备了在他之前中国思想所没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因此无疑应该重视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充分理解朱子学,也是事实。[2]吾妻氏认为,朱子学作为中国近世以降的思想母胎,其思想史地位固然重要,只是,这当中尚有许多可供开发的论题,就中国脉络而言,可关注朱子的教育论及其实践;而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多可着眼在朱子学当中的礼学与礼制的研究上,如《朱子家礼》对于“冠昏丧祭”四礼的规定等。
同时,吾妻氏亦提醒我们,应当注意朱子主张“理一分殊”当中“理”的普遍性,而且他把“理”比作朱子学自中国远播至东亚世界后所形成的普遍性之“理”,换言之,即关注朱子学在域外的发展。朱子学之“理”于东亚世界形成的普遍性,这种观察并非吾妻氏孤明先发。事实上,早在日本德川时代,由僧入儒的藤原惺窝(1561—1619)在其《惺窝问答》《舟中规约》等文章,甚至于替幕府起草的官方外交文书《致书安南国》中,再三申阐朱子思想体系,以由“理”作为命题所组构而成的普遍主义,借以强调此“理”、此“性”系人与生俱来即有,并不为各国不同的文化风土所囿限。是以,吾妻氏认为能自惺窝的认识当中窥见,朱子学在当时东亚世界中被广泛接受,具体的表现在于书院的教育、礼制的规定等两大层面,其中,《朱子家礼》更是成为东亚世界所广泛采纳的礼仪准则,即使时至今日,仍可将这套礼节视为“活”的传统。[3]
如上所述,吾妻重二教授揭示了《朱子家礼》对于中国,甚至东亚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性,相较于此,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则是以《朱子家训》作为分析文本。朱氏首先将《家训》与中国历代著名的家训做一比较,他认为,《家训》并不如同其他家训洋洋洒洒,动辄载录数万言的长篇巨制,反而是颠覆旧有的典型,其关键乃在于《家训》全书仅317字之多,便于记诵、利于传播,据此,朱氏指认《家训》呈现出它的“普世”性。[4]再者,《家训》本来虽只是在朱氏家族内部流传,但它以通俗、精练的文字来加以缮写,更是具体指出作为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约束,从而打破既有的界域,证明了其“普世化”的意义。
二、专书
关于2014年度朱子学相关研究的专书,若算上翻译本,则可指出以下三本,分别是:李蕙如的《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胡春依的《朱熹、袁甫与黎立武的四书诠释及其比较》,以及由日本学者佐野公治著,庄兵、张文朝翻译,并由林庆彰进行校订的《四书学史的研究》。限于篇幅,以下仅就李蕙如一书略做介绍。
李蕙如《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一书,系由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改写出版,全书共分六章,以及附录一篇,章节架构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第三节 研究之方法与步骤
第二章 许衡其人及其书
第一节 许衡生平传略
第二节 许衡著作介绍
第三章 许衡对先秦儒道思想之评论
第一节 对孔孟思想的评论
第二节 对先秦道家思想的评论
第四章 许衡推动朱学官学化的历程
第一节 发轫期
第二节 发展期
第三节 完成期
第五章 许衡的影响及历史评价
第一节 许衡的影响
第二节 历代对许衡的评价
第六章 结论
参考书目
附录
以全书的章节安排来说,作者将重点安排在第四章,即关注在宋元鼎革之际许衡(1209—1281)是如何在异族的统治下,致力于程朱理学之推动,后使其官学化的过程。作者指出,理学官学化运动,在早先的南宋时期即已产生,如真德秀(1178—1235)以及魏了翁(1178—1237)曾倡尊理学,但是,终宋之世,理学的官学化终究没有达成,即使理学在理宗朝时得到官方的认可,却始终未能将其制度化。作者认为,这种理学官学化运动,主要系出于许衡的擘画。[5]
作者指出,许衡作为一个汉人儒者,他试图在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体制下,通过与政治力量合作的方式,使国家步入正轨,而这首要工作便在于“恢复儒治”,即“行汉法”,如采取通过经筵讲学、以儒道治国,乃至推动教育、使国子监书院化等具体行为。此外,许衡更致力于朱子学的通俗化,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易简”的学术诉求上,如他在解释“道”字时说:“众人之所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其认为“道”应该是一贴近众人之事,举凡日常生活所需之盐米物资、人伦日用之事,皆是属于广义而言的“道”之范畴。[6]
许衡对朱子学的继承,较具有思想体系的脉络,这主要可从他的“四书”学上探知。作者指出,许衡论《大学》时,特重“修身”,故有“大学之教最紧要全在修身上”之语,又尤当许衡将此“修身”工夫明确地归于皇帝之时,借以强调君王本有的“絜矩之道”,据此,作者认为许衡之所以重视“修身”之教的原因,其关键在于“修身即是正心,身正即是心正,因此,一心正则家正、国正,心正是天下的体例”,许衡认为正心是“修身”的“根脚”,同时也是治国之根本。关于“修身”所应因循的路径,许衡则遵循朱子所言,认为应系于“敬”一字,但许衡认为此“敬”并非单纯讲求内在修养,而是必须内外兼具,是以他将其分疏为二:其一为“心术正乎内”,其二则为“威严正乎外”。[7]
论及朱子学最核心的命题“格物致知”时,许衡则有其不同的见解。作者指出,许衡认为“正心”之前尚有“格物”“致知”“诚意”等工夫,但此三者皆必须在“心”上下功夫,据此,如许衡在解释“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以及“致知在格物”两句之时,皆重视“心”的意义及其作用,用作者的话来说,即“主张致吾心之知,穷吾心之理,把格物致知和尽心知性联系起来”。[8]如此,在“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的先后问题上,许衡即一反朱子之道,其所主张则是“分知行为二事、提倡真知力行,主张知行并进、先务躬行”,这同时也构成许衡学说当中的重要命题。[9]
提到《论语》与《孟子》之时,作者指出,许衡主要把儒家的天道观念放在政治问题中进行讨论,故而当许衡论及天命,尤其是着眼于“命”的观念时,自然不会是术法家所言的宿命,更不会是释、道思想下的范畴,他所指摘的是“不可变易的自然秩序”,这一点,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于封建社会的认识上,他将封建社会视为自然秩序。[10]至于许衡对《中庸》的理解,他师法程朱,将《中庸》之道视为“着实有用”之学问,并以此来批判佛老的虚无之教。此外,许衡虽同样接受程朱有关“理”的说法,但他更重视的是将“理”的作用与价值落实到具体的事物上,而非仅是作为万物的发生源。换言之,即许衡重视的是“物”与“理”两者之间的“不可相离”。[11]
许衡对于朱子学的绍述、传衍,理解与批判,均可视为是他推行朱学的发展期。然而,元代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完成,主要落在元廷将朱注“四书”正式颁订为科举制度下的考试定本,是年为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意即,终许衡一生对于程朱理学的推行,但到其辞世之前,科举制度皆未能施行,不过,许衡在推动程朱理学官学化过程中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在科举制度颁行的同年,许衡也得以配祀于孔庙,官方更成立书院以提倡许衡之学。[12]职是之故,就以元代官方对于许衡功业如此重视的情形来看,可见他对朱学传承以及朱学官学化的贡献,在政治、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具其重要性。
三、期刊论文、专书论文
在2014年度的学术期刊中,有将朱子学相关议题的探讨订为专号,篇中亦收录有关朱子思想的精彩论著,如《哲学与文化》在第41卷第5期中制作了“朱王对比专题”,其后,在第41卷第8期中又制作了“韩国儒学的人物性同异论之研究专题”,此两期专辑所收录之论文,主要涉及朱子学的比较、诠释与再现(韩国朱子学)等课题,同时亦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新视野。
此外,在专书论文的部分,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在其新书《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中,收录了《儒家历史叙述的特质:朱子历史叙述中的圣王典范》以及《儒家历史解释的理论基础: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两篇修订后的旧文。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则是在其主编的《自然概念史论》当中收录《理学论述的“自然”概念》一文。另一方面,金永植教授探讨朱子自然哲学的相关研究亦被翻译成中文,如有《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与《朱熹“格物”与“致知”方法论中的“类推”》两文,被收录在他最新出版的《科学与东亚儒家传统》一书当中。[13]
2014年中国台湾学界有关朱熹思想以及朱子学的研究论文,殆可粗分为五类,以下,依各论文论旨做一略述:
(一)朱熹思想与观念问题
本年度关于朱熹思想与观念问题的研究论著,可以举出许朝阳《挂搭与相衮:朱子的理气型态及其对“恶”的处理》、王雪卿《朱子工夫论中的静坐》,以及冯兵《情感性·宗教性·实践性——朱子礼学观的三重维度》三篇文章。
就中国台湾学界对宋明理学的解析与分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属当代新儒家牟宗三(1909—1995)。牟宗三主要将理学归类为两种型态:其一为“即存有即活动”,二则为“即存有不活动”,据此分系,朱子的思想系属后者。许朝阳一文即尝试在此框架下提出不同的看法。在通过与印度数论派哲学中的“神我”(purusa)与“自性”(praksti)对比之下,作者指出,朱子之理呈现两种不同的型态,首先,朱子在论现象的发生时使用“理挂搭在气上”之句,以“挂搭”来指认理气关系的确符合理不活动的推论,此系理的“消极参与”。但是,在朱子的认识里,理亦内寓于事物当中,即所谓“天地万物莫不有理”,故可推知善之事物,有其善之共相,恶之事物亦然,据此,作者指出朱子理气论下的“相衮”型态,此则理之“积极参与”,是为第二种型态。因此,朱子之学并非如数论派哲学所申阐的,仅将“神我”当作一不参与经验世界运行,漠然旁观的他者,是为“完全地不活动”。总此推论,作者说:
为了维持本体至善;朱子的理气论倾向“挂搭”型态;但为了使理具体呈
现于现象,则又倾向“相衮”型态。
由此可见,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之下,理仍是必须参与经验世界的活动,那么,理在这参与现象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活动的可能。[14]
朱子的工夫论与其思想的联结以及实践,同样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雪卿论朱子静坐法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朱子深具儒家色彩的静坐法。所谓静坐,并非儒家本有,此法征于释、老二氏,亦多有所见。朱子对于静坐工夫的认识,则主要来自于二程。作者认为,对朱子而言,静坐法虽非儒门之本质工夫,但却是重要的工夫。也因此,他必须鉴别儒门静坐法与二氏之异同,如不效法佛教坐禅时的趺坐,亦不从道家静坐的数息之法,因为在朱子的认识当中,儒家的静坐不需刻意强调坐姿与调心、气之法,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坐。因此,作者更进一步地指认出,朱子静坐法的特色,其要有二:首先,是将静坐收摄于“主敬”之工夫下,强调“事”,“事”来应事,无事则静坐,敬贯动静,将“主敬”之工夫运用在“事”上。其次,朱子对禅宗顿悟说提出批判,反对其顿教“直证心体”“逆觉体证”等类的心学工夫,他所肯认的静坐法乃是在“格物穷理”工夫中扮演辅助性的角色,故而又常与读书一事对举。据此而言,作者总结出,朱子工夫论中的静坐法应该是“涵养本原”工夫,且朱子的静坐法与他所主张的“格物穷理”关系密切,此则可与道理、读书等诸事并举。[15]
朱子礼学的形成,与其理学体系可谓是互相辉映。冯兵认为,此两者的会通可以自三个层面进行观察,他在文章的摘要中便如此说明:“朱子礼学的情感性维度主要展现了儒家理学重视情感体验的人文关怀精神,宗教性维度显示了朱子礼学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过程,而实践性维度则标明了朱熹对礼学实践的现实有效性的关注。”作者在情感性的论述当中,指摘出如妇女改嫁等问题,以昭示朱子理学的核心价值;其次,在宗教性,则以鬼神论为讨论重点,尽管朱熹的礼学中同样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足以构成为宗教体系;最后,于实践性的探究中,作者指出,朱熹礼学的实践系根据前述的情感性与宗教性叠加而成,此两者虽看似矛盾、难以融洽,却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到有效的会通。[16]
(二)“四书”与经学相关研究
有关“四书”与经学相关研究,计有姜龙翔《论朱子诠释<国风>怨刺诗之教化意涵》、劳悦强《<论语><先进>篇“屡空”辨》以及陈逢源《从五贤信仰到道统系谱—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圣门传道脉络之历史考察》三篇文章。
姜龙翔的论文谈及朱熹对于《诗经·国风》的诠释,尤其是重点关注了所谓的“怨刺诗”。作者指出,朱熹基本上没采用《诗集传序》的持论,将《国风》仅看作是讽刺时政之作,朱子对于《诗经》的诠释,主要关注它的教化功能,因此,他将《国风》视为性情之作。盖《诗经》所录之《国风》,其所载言,主要是人民真实心声的吐露,故有益于为政者的执政参考,着实有重大的意义。总此上述的分析,作者指出,朱熹对于《国风》中怨刺诗的诠释大抵可以得出两种结论:其一,朱子在孔子既有的“《诗》可以怨”的原则下,更加发挥了“怨而不怒”“怨而能正”来补充对《国风》的认识;其二,朱子不采《诗集传序》所论,乃是为避免读者误解《诗经》原本讲求教化、温柔敦厚之旨意。[17]
宋儒治经典之时,其态度多趋向疑经,甚或有改经之作。劳悦强一文,则是从经学史、思想史以及文献学等脉络来对朱熹于《四书集注》中的解释提出质疑。作者的重点聚焦在朱子对《论语·先进》中孔子论颜回“回也其庶乎,屡空”这句话的理解上。其中,“庶乎”为“近道”之义,此系学界公认之通说,殆无疑义。问题主要出在对“屡空”的诠解上。作者指出,自汉代以降,“屡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遵循汉儒所言的“空匮”,二则是何晏(195?—249)别开生面的“虚中”之说,何晏虽别立新说,但他同样循汉儒主张的“屡空”,并以“虚中”为另解,即两者并存。相对而言,在朱子《论语集注》成书之后,其对“屡空”之解,采“空匮”解义,却反倒排斥何晏“虚中”之解,原因在于,朱子指“虚中”为“老氏清静之学”,进而加以批驳。总此推论,作者认为,若依照朱子的解法,基本上并不符合孔子于《先进》篇中所欲阐说的原旨,且朱子更是误解了何晏“虚中”的寓意。[18]
儒家讲求圣贤系谱的传承,主要自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始,到了唐代韩愈(768—824)又有所发挥。陈逢源一文则是在处理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当中对于道统系谱的重新确立。北宋时期,士大夫对于儒门道统传承的看法多受韩愈的影响,并认为孟子得到表彰是受到韩文公重新订立道统系谱的影响,是以,孟、韩二人经常为士人所并举。孟、韩之后,又增列荀子(前313—前238)、扬雄(前53—18)、王通(584—617)三人,于此便形成五贤信仰,五贤信仰又以石介(1005—1045)的推崇为甚。然在王安石(1021—1086)主政之时,完成了一系列孟子的升格运动,使孟子得以配享孔庙,遂脱离了原有的五贤信仰。作者认为,尽管王安石对于尊孟有功,但就他对孟学的理解,尤其对“性善”之体认不深,以致变法失败。然这样的反省其实早在二程时即已提出,二程列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儒门的传道系谱,认为唯有重视性善才是儒学的价值核心,但终北宋一朝仍是不脱以五贤信仰为主,直到宋室南迁这一变局形成之时,方才刺激士人对道统系谱进行重新思考。作者指出,南宋对道统重新提出认识的,当以朱子为集大成者,朱子自儒门经典中重新寻求答案,终于在《中庸章句序》得出答案,揭示“尧、舜、禹、汤、文、武圣人相承结构中,续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传道系谱,彰显儒者遥契尧、舜,志继孔孟的情怀”,此为后人所周知的道统系谱,足见历代道统的积累,主要亦是根据朱熹建构的成果。[19]
(三)朱子的史观与史学
本年度讨论朱子的史观及其史学的研究,计有胡元玲《朱熹对宋王朝南渡变局的省思》以及黄俊杰的《儒家历史叙述的特质:朱子历史叙述中的圣王典范》《儒家历史解释的理论基础: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三篇专论。
综观朱子生涯,多是从事讲学,于乡里之间活动,但这并不表示朱子就此与政治无缘,《宋史》载朱子一生立朝仅四十余日,但这并不妨碍朱子本身对于政治的观察,至少就宋朝当代的历史是如此。胡元玲一文即是从宋王朝南渡的历史事件来考究朱子的省思态度,主要从朱子对于宋代历史(评论徽宗、钦宗北狩;批评高宗南渡与建都;批判秦桧误国以及陷害忠良;检讨隆兴北伐与和议;维护正统立场等)的观察来展开论述。据此,作者认为,朱子在“内圣”讲求遥契圣贤的修养层次,其造诣固然可观,然就“外王”而言,亦多可见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20]
朱子除了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观察外,他更将这种眼光投注于历史的发展,黄俊杰一文,则是试从朱子的历史论述中爬疏他的圣王典范。作者指出,宋儒的历史论述中,多是透过特定的史实来进行叙述,借以提炼事中之“理”,而这些“理”则泰半呈现在圣人的行谊之上,因此,就以宋儒的史识而论,朱子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朱子认为挖掘史事中的“理”必须先阅经典,次阅史籍,作者在统括这段认识后,进行如此诠解:
朱子之所以说“经”比“史”更重要,主要的含义是:读史的目的在于即“事”以穷“理”,史实的究明只是手段,史理的抽离才是目的,而经由抽
离之后的“理”主要见之于经书之中,所以“经”先于“史”。“即史以求理”中的“理”兼具内在与超越等两种性质,故“理”不脱离史实,但又超越于史实之上。最后,作者认为宋儒乃至于朱子历史论述中的圣王典范,其所运用的方法多是“从历史论述提出哲学命题”,从而成为他们的核心价值。[21]
朱熹关于历史的相关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其门人贯彻他意志所撰写,诉诸名分、正统的《资治通鉴纲目》。然而在朱子的其他著作当中,亦可见到一些他对于历史的观察,黄俊杰则侧重研究朱子对于中国历史的诠释。作者首先指摘出朱熹推崇三代的史观,是为“崇古的历史观”,认为自三代以后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堕落的态势,这样的转折主要是自秦代开始,原因在于自秦代所发轫的政治体制,呈现出“君尊臣卑”的关系。朱子的史观聚焦在“势”的转变,如由周至秦的“事势之必变”以及汉晋之间的“因其事势,不得不然”,两者皆然。接着,作者指出,在朱子的认识中,能够驾驭历史之“势”的只有人,因为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作者还通过朱子“理一分殊”的特点来考察他的历史理论,朱子认为历史虽遵循着“理”来发展,但这种“理”的体现只有历代圣贤能够掌握,不免也忽略了群众对于历史的作用。总此论述,作者认为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主要是以三代作为批导现实的精神杠杆,通过理想化的三代来评骘历史,企图将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镕铸在一起,这大概是朱子史观的特色。[22]
(四)朱王比较
朱陆异同以及朱王异同,此间所涉及的经典诠释、义理析论,向来是研究宋明理学重要的议题。而就2014年度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主要有蔡家和《朱子与阳明的孟学诠释差异之比较》以及黄信二《从朱子与阳明论蒯聩与卫辄比较朱王之“礼”论》两篇文章。
蔡家和通过朱熹和王阳明(1472—1529)对于孟学的诠释来展开论述,作者以(1)“尽其心者章”的诠释、(2)孟子学的义内义外问题、(3)性属理还是气、(4)性是善还是无善恶等,作为朱王之间诠释的相异处进行了比较。就(1)而论,作者指出,朱子诠释《孟子》时,主要以《大学》的架构进行通贯,重视先知后行的为学次第;相对于此,阳明则不重为学次第,但同样是以自倡的良知学来诠释《孟子》,据此,《孟子》成了一个过程的工具,朱王只是通过《孟子》来发明自己的学说。就以工夫论一事而言,作者指出,朱子论工夫时分居敬与涵养为二,但阳明的工夫只着眼在致良知一个工夫上,亦不相同。以(2)来说,作者认为,阳明的说法较符合孟子原意,因为朱子的体系扩及到宇宙论范畴的天地万物,故其义在内也在外。关于(3)的课题,孟子本来没有将性分为形上、形下之区别,但朱子因在佛教传入后,容摄其思想体系来开展新儒学,故以理气诠释。就性为理气和这点的说法,朱子较近似于孟子,阳明持论则是弥补朱熹的二元区分。至于(4),作者认为,讨论到性为善或是无善恶的问题时,朱子的诠释较近于孟子,因为阳明将善分为绝对善与相对善,此系儒家在面对佛学问题下,进而抟成的一种思维,可视为阳明自身的创造,但却远非孟子本意。[23]
黄信二一文,则是就朱子与阳明对春秋时卫国蒯聩与卫辄父子之间的王位之争是否合乎礼之准则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从两者释“礼”的差异来进行分析,朱子的立场在于贯彻某种伦理价值,使其合乎礼;阳明则是紧扣着使礼能被彻底执行的道德动机。据此,作者认为朱王之间对于礼之过程的“应用”与“发生”的重视程度,有其不同。以蒯聩与卫辄一案来说,阳明偏重父子之间的感受,故其重视礼“发生”时情感的考虑;朱子则侧重在父子之间的关系,“应用”并严守亲亲义理,借以提炼出某种普世价值。作者指出,阳明认为,应使蒯聩与卫辄相让为国,恢复良好的父子关系,重视人情天理。朱子则认为,蒯聩与卫辄皆不应登位,如此便不会有后来相争王位等事,应重视礼之意志的执行,但更强调其中的节制意义。最后,作者在比较朱王二者后认为,其二人对礼认识的差异仅在于思想体系中对于体用关系的侧重程度不同,并不代表他们的理解有所误差。[24]
(五)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
近年来,汉学研究的崛兴,同时也使得其在域外儒学等相关领域受到重视,就这一点来说,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更是不可忽略的重点,就历年来的研究趋势而言,主要聚焦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2014年度中国台湾学界关于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出版同样丰富,其中尤以韩国朱子学的研究为最多。
1.日本
关于日本儒学研究的文章,本年度业已出版的论文,计有张文朝《渡边蒙庵<诗传恶石>对朱熹<诗集传>之批判——兼论其对古文辞学派<诗经>观之继承》以及傅锡洪《“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探微——有关儒家天人合一之学之建构与解构的一项考察》等。这两篇文章所关注的课题,均是聚焦在古学派对于朱子学的批判上。
就日本汉学的发展来说,因其特有风土环境、政治思维的影响,从而长成的古学派,他们所欲申阐的论点,主要关注点在对朱子学的解构上,其中又以荻生徂徕(1666—1728)的萱园学派(古文辞学派)影响为大。张文朝一文的切入点则放在萱园学派的渡边蒙庵(1687—1755)对于《诗经》的诠解上。盖渡边蒙庵主要师承太宰春台(1680—1747),又为荻生徂徕之徒孙,是以,就他的《诗经》观而言,同样深受两者的影响。作者以蒙庵的《诗经恶石》为分析文本,并指摘出它非但不是如历来研究所指认,为其师春台《诗经膏肓》的补注,反而能从其中窥见古文辞学派中治《诗经》的态度以及对朱子的批判。不论是春台的《诗经膏肓》,或是蒙庵的《诗经恶石》,基本上都将《诗经》视作一部诗选。作者认为“古文辞学派学者大多有挟汉儒去古未远之势,以制朱熹新注之说的倾向”,故此,从徂徕到春台再到蒙庵的一贯立场,均在取消《诗经》的经书地位,并通过学习《诗经》中的古文辞、掌握个中揭示的人情,以供施政之用。此举主要是以“知人情”来供为政者参考,不若朱子以《春秋》的“劝善惩恶”来阐释《诗经》。再者,古文辞学派认为经典为圣王之作、安民之道,故其重视实学层面,这也是为什么蒙庵要批判朱熹以持敬、义理、治心来解《诗经》,因为此并无助于现实政治治理的需要,是为无用之学。[25]
相较于对经典诠释的批判,古学派于思想体系对朱子学的解构,亦有所见。傅锡洪就朱子的鬼神观来考究它的成立,以致后来儒学东传日本后,遭到江户时期古学派彻底解构的过程。一般而言,常人多将鬼神析分为二,其一为“在天之鬼神”(即阴阳造化),其二则是“祭祀之鬼神”(即神示祖考),但朱熹认为,在儒家经典中,此两“在天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是统一的,而非“二事”。若鬼神是“二事”,则人道不能本于天道,儒教的天人合一之学将由此被截断。然这样的认知来到日本,力图解构朱子学的古学派学者,便严分鬼神祭祀与现实人世的距离。作者指出,古义学派的伊藤仁斋(1627—1705)首发其端,他并不否认阴阳之鬼神,却也不谈及祭祀时的鬼神感应,对于鬼神是否为“二事”采“不必”的立场。古文辞学派的荻生徂徕,同样反对鬼神感应之说,对仁斋之说亦提出批驳,因为他认为鬼神并不可知,只要遵循先王之道即可,他对鬼神的认知仅限于天神人鬼作为祭祀对象的鬼神,反对形上的阴阳造化,因此,就鬼神是否为“二事”而言,他采“不能”的立场。怀德堂的中井履轩(1732—1817)虽不否认阴阳鬼神之存在,但就祭祀而言,他认为鬼神“不在”,重要是己身的孝敬之心。于此,朱熹所持论的“在天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并非二事,在江户中期开始受到古学派或批判、或痛诋,终将其彻底析解为二。[26]
2.韩国
韩国儒学的发展,自进入朝鲜时期(1392—1910)后,即已确立以朱子学为国学,将其定为一尊,故有关朝鲜时期的儒学研究,多是指向以性理学为宗的相关研究,讨论的重点亦多是围绕在对朱子思想的诠释上。就本年度的韩国儒学研究而论,有姜真硕《栗谷哲学与人物性同异论之成立》以及李演都《湛轩洪大容的“人物均”论探究——朝鲜后期人物性同异论争的演变与其意义》等讨论人性、物性同异论的专文,另有姜智恩《东亚学术史观的殖民扭曲与重塑——以韩国“朝鲜儒学创见模式”的经学论述为核心》一文,则是尝试梳理20世纪初韩国学界对于17世纪朝鲜儒者思想世界的过度扭曲,借以廓清对朝鲜学术史观的认识。
韩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两大论争,其一为“四端七情论争”,其二则为“湖洛论争”。湖洛论争,主要是湖学与洛学两个学派对于朱子学诠释的不同立场所产生的,而人性、物性同异论便是两派论争的主流。姜真硕一文即揭示了人性、物性同异论争,其实与李珥(号栗谷,1536—1584)的哲学思想诠释密切相关。即在此议题上,栗谷哲学居其中心的地位。作者认为,16世纪由栗谷提出“理发气乘”和“理通气局”建构己身之哲学体系,且其中的“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成为17、18世纪栗谷后学开展人性、物性同异论争的基本骨干。作者指出,栗谷及其门人都着重在探讨气的思想,“气局”突显了他特有的思维。栗谷认为,人、物之不同除了表现在气质外,其理禀亦不相同,故说万物“不能禀全德,心不能通众理”。而就气禀来说,作者认为:“人不能不有气质的限制,而同时具备虚灵洞彻之心,因此能够克治气局限制,变化自己。”因天生气禀之有别,是故人有圣俗之分。由此观之,栗谷之“气局”说不但证明了人性、物性之有别,更进一步地阐说了人、人性的异论。[27]
如果说人性、物性同异论争是以栗谷的哲学思想为肇端所产生的,那么,这种论争的转折则主要可自洪大容(号湛轩,1731—1783)谈起,李演都的研究即关注于此。作者指出,在18世纪初湖洛论争进入高峰期时,正好是洪大容活跃的时期,而此时朝鲜性理学的发展,已然走向在理学、心学的基础上,同博学结合的趋势。湛轩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故其重视实学,是以,就他所主张的气论而言,他主要只以气之活动来阐释宇宙的形成与变化,并且对朱子学中理之主宰性提出反驳,但并不反对理的存有。作者指出,湛轩思想中理的地位主要是:“基于对于自然界的经验上之普遍原理。”此气一元论的立场,系湛轩理解人物论的重要前提,作者通过湛轩在《医山问答》中的《人物心性论》以及《心性问》《答徐成之论心说》等文,揭示了湛轩讨论心性论的关键词,乃在“以天视之”和“人物均”。就前者言,湛轩认为要“以天视之”,方可超越“以人视物”“以物视人”两种观点。至于后者,作者则指出“人物均”的概念与湛轩之气论息息相关,湛轩持气一元论,故其认为心亦是由气构成,但湛轩认为人性与物性在心的本体上并没有区别,即他主张的“人物心本同”,扩张洛学本有对心论的认识。至此,作者指出,湛轩已然摆脱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价值,且他是“站在物活论的自然观之立场来看待人与物的同等关系”,此举近似于现代以科学角度来对自然万物进行观察,同时也开启了朝鲜后期性理学的转向。[28]
朝鲜王朝可说是以朱子学立国的政权。但是,将朱子学定于一尊的影响,并不止于学术层面,在政治场域亦有所见,如国家政策、礼制亦多遵照朱子的训示。而在日本殖民时期(1910—1945)的韩国学界,则认为韩国之所以沦落于此,应该要彻底批判将朱子学定为国学一事。但这样所谓“彻底批判”并不免启人疑窦,且有失其学术观察的客观性,姜智恩即尝试就东亚来作为观察视域,借此重构17世纪朝鲜经学史的图像。作者指出,日本殖民时期,日本的御用学者(如高桥亨、井上哲次郎等)多是贬低朝鲜儒学,指其缺乏创造性,不若日本江户时期之古学对朱子学提出挑战,直接迈向近代化。是以,就20纪初期的韩国学界而言,有鉴于过度提高朱子学地位进而导致亡国,故当时的知识分子多采取以下两种策略:“其一,是批判只信奉朱子学的儒家,其二则发掘‘非朱子学’的历史人物,来作为‘近代先驱’而加以赞扬。”以此来反击日本官方的论述,作为拯救国难的新的学术史观。作者在梳理、比较日本御用学者与韩国学界的论点后认为,20世纪初以如此“矫枉过正”的态度来批判朱子学,其实并无助于理解17世纪时儒者的思想世界,其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的儒学发展模式不同。日本为武士政权,故重武治,且并没有施行科举,儒学的影响性并不大,相对于此,韩国则是重文治,以科举取士,儒学(朱子学)的影响可谓是十分深刻,即使无官职之士人亦可对国政提出谏言。因此,以日本经验来贬抑朝鲜儒学,恐怕不能成立。再者,作者指出,朝鲜的儒者并非完全尊奉朱子学,他们亦自朱子矛盾之处,提出独创的见解,并找出朱子另一说法并陈,此即作者定义的“朝鲜儒学创见模式”。准此,17世纪时朝鲜的学术空气并不如20世纪初学者所认为的“盲从朱子学”或是通过“批判朱子学”进而得到更新,相对地,反而是更加仔细钻研朱子学,始能具其新的诠释。如此,作者认为,必须重新正视朝鲜儒者对于朱子学诠释的独创性,以免走入被扭曲的经学史观当中。[29]
综观本年度中国台湾学界关于朱子学的研究,由于国际研讨会的举办、学术期刊推出朱子研究的相关专辑,甚至于学术交流的增加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说是十分丰硕。本年度朱子学的研究议题,除了对于朱子学术、思想观念提出新的见解外,亦旁及他的史观、史学以及“四书”学等,甚至与阳明之间进行比较,总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都丰富了对朱子学的探掘,使吾人能一窥堂奥。
近十多年来,台湾地区的儒学研究开始尝试以东亚作为视野,借此视角来观察儒学于东亚世界中所呈现的多元样貌,这其中尤以朱子学的影响最为深刻。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展开,此似可援引黄俊杰教授借朱子“理一分殊”的论述来加以阐说。[30]即将中国原生的朱子学比喻为“理一”,将域外朱子学视为“分殊”,并自“分殊”之中觅得“理一”,相互呼应,产生对话、交流的可能性。我们亦可从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中,窥见这些存于域外并且生机盎然的思想体系。如日本古学派(古义学、古文辞学)对于朱子学的解构,他们讲求实学,反对形而上的“理”,在日本的风土环境下证明了已有的思维系统。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的是,本年度有关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数量明显增多,尤其以朝鲜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最多,他们主要通过会议论文、期刊论文的形式被介绍到中国台湾学界,从而充实了对韩国儒学的认识。如前述提及湖洛论争当中的“人物性同异论”,以及姜智恩论述下的“朝鲜儒学创见模式”等学术史的发展,均是在朝鲜特有的历史环境下所成形的。
总括前述所论,我们可以从朱子学在东亚世界遭受到不同的际遇,来重新审视各个政权、文化体系之间对于儒学受容的影响(诚如姜智恩一文所揭示的),亦可通过此一比较来反思中国原生朱子学,乃至近世以降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整体构造,以为他山之石。尽管对中国台湾学界而言,东亚朱子学的研究呈现逐年增加之势,但唯一可惜的是,本年度并没有针对越南朱子学进行专门探讨的论著。
2014年香港朱子学研究综述
——以“朱熹与宋明理学”研讨会为焦点
吴启超
2014年12月4日至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次“朱熹与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会议云集中国、韩国、新加坡的朱子学专家学者共21人,发表论文20篇(其中一篇由二人合撰),可谓去年香港朱子学界一大盛事。本文将介绍评述当中几篇由香港学者发表的论文,让读者了解过去一年香港朱子学研究的进展及其今后的动向。
与会者中,有三位在香港的大学任职,包括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陈荣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吴启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此外亦有三位出生于香港而现正任职于香港以外的大学,包括李瑞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杨祖汉(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劳悦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以下依次介绍这六位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和观点。
(1)郑宗义教授为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现任主任,发表论文题为《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众所周知,当代新儒家牟宗三(1909—1995)的朱子哲学诠释既体大思精又别树一帜,其由仔细的文献梳理和精密的理论剖析而得出的论断,例如指朱子为“儒学之歧出”“道德之他律”“泛认知主义”等,至今仍为学界所热议。郑宗义一文则提出,同属当代新儒家的唐君毅(1909—1978),其朱子哲学诠释散见于《中国哲学原论》之《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书中,论述之集中程度及篇幅或不及牟宗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则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手的诠释体系”。是故,该文即旨在“通过比论唐、牟对朱子哲学的不同看法,来将唐氏提示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发挥与建构”。但作者随即强调“比论之意义,固不在分辨高下,而是在于能对朱子哲学更求善解”,表示该文所从事的乃客观持平的学术工作,而非为争门户。
笔者理解,郑教授一文的关键议题为“朱子哲学能否承认‘心体’(‘心’本与‘理’为一)之观念”(牟宗三对此持否定立场)。若能,则朱子之“心”自非如牟宗三所理解般,纯然只是一“认知心”,而其理论亦非如牟氏所指,为“泛认知主义”(以“认知”决定“行动”)并存在“道德动力不足”的困难(仅靠“格物穷理”的认知工夫不足以推动道德实践)。再者,朱子哲学中一些重要概念如“敬”“真知”等,亦将可得一既有别于牟宗三而又更为妥善的诠释。换言之,“论证朱子哲学有一‘心体’之观念”可说是全文立论之基石。
为此,郑教授详引唐君毅文字,指出唐氏肯定朱子有“心体”之观念。更重要者,郑教授并非仅仅引录复述唐氏之言,而是进一步通过朱子原文来为唐氏的诠释予以补充、强化和证明,使得全文读来持之有故,推论稳健。可是,会议上亦有学者提出疑问:首先,唐氏固然有使用“心体”一词,但其用法是否同于牟宗三,指一“本与‘理’为一”的“心”?其次,郑教授虽然提出朱子有“介然之觉”和“立志”等说,以证明朱子确可安立“心体”之观念,但正如牟宗三曾指出,朱子立论常有些“不自觉的因袭语”——不自觉地因袭儒学传统内(尤其孟子)的用语,因此,“介然之觉”“立志”等语,从朱子口中说出来,其真实意义到底如何,恐怕仍需穿透字面而做进一步的解读。但话说回来,郑教授一文虽仍有可议之处,然其试图立足于唐君毅而建立一套完整而周延的朱子哲学新诠释,实亦为朱子哲学研究之另开新局踏出了一步。
(2)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荣开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朱子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环绕其<四书>解说所作的观察》。全文长达41页,极具分量,以朱子的《中庸章句》第二十三章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为焦点,进行了非常细密的剖析,可谓强探力索。笔者撰写本文前,曾与陈教授通信,得知该文乃其有关朱子《中庸》注研究的延续。该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目的乃在剖析《中庸章句》所强调之严密结构,从而揭示其中未为熟知的义理内涵。陈教授并向笔者表示,该研究目前尚在推进当中,待他日把计划内的文章写就之后,将汇辑成编,以便学者参考。以下即此项计划所已发表的论文:
①《朱子<中庸>首章说试释》,收入《结网篇》,1998年,第407—488页;
②《读大槻信良氏有关<中庸章句>典据的研究》,收入《结网二篇》,2003年,第495—530页;
③《朱子<中庸>结构说(上)》,收入《儒学、文化与宗教——贺刘述先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2006年,第63—96页;
④《朱子<中庸>结构说(中)》,收入《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2009年,第429—468页;
⑤《首尾接续,血脉通贯——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章缜密结构的分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五辑,2009年,第151—184页;
⑥《朱子对<中庸章句>“诚明”章的剖析与解读》,收入《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1年,第610—624页;
⑦《朱子对<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的解读》,收入《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第208—232页。
回到陈教授此次会议发表的文章。该文聚焦于朱子对《中庸》第二十三章首句“其次致曲”的解释:“‘其次’,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故题为《朱子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陈教授亦表示:“为了充分掌握朱子对此句经文的理解,本文又大幅引用了他对《论语》《孟子》等书有关篇章的解释。”是故该文在正题之下再加上一副题:“环绕其《四书》解说所作的观察。”
依笔者理解,陈教授一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探讨“致曲”这种属于“大贤以下”之修养工夫的背景、目标和依据。“致曲”的背景就是人的“天性”与“气禀”:凡人皆有纯粹至善的“天性”,唯其落实于人身,即不能不受“气禀”的干扰(尤其是“大贤以下”之人),而有种种“曲”的表现。目标方面,“致曲”的进行有两种向度:“量的向外推展”(把“善端”横向地推展至生活上的时时刻刻)和“质的内在提升”(把“天性”之呈现趋于精纯,愈来愈摆脱“气禀”的夹杂)。陈教授认为,两者相较,后者更属“致曲”工夫的重点。依据方面,整个“致曲”工夫的历程,不论是起点(察识善端)、归宿(善端之充满)或其间的过程(善端之推扩),无不以本然内具的“天性”为依据。
第二部分,陈教授集中讨论朱子眼中“气禀”在修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根据相当充分的朱子原文(尤其是朱子对《论语》《孟子》的解释),表明朱子对“气禀”之于道德修养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有非常深刻的照察,例如令人在道德实践时产生潜在于隐微之间的不纯意念、令人知而不行(明知其是或非,却又当为而不能为或当止而不能止)等。但另一方面,陈教授又指出:“尽管如此,朱子之以气禀言曲,实也反映其不以气禀为全然的不善。在他看来,天性的展现固不可能离乎气禀,作为天性得以体现的载体及其所能充扩至极的据点,气禀更有其积极的意义。”
(3)笔者本人于此次会议交出了《是非之心在朱子哲学中的特殊性》一文。拙文“尝试揭示朱子对于‘四端之心’中的‘是非之心’的特殊看法,进而指出,我们若能注视这点,将可对朱子的某些论述(尤其工夫论)、立场和论证得到更好的理解,亦可更准确地测定朱子哲学所可能触及的某些哲学议题”。拙文因而分为两部分,先讨论朱子对“是非之心”的特殊见解,继而探讨:“基于这种见解,朱子在工夫论上可以对其儒学内部之论敌(本文将以湖湘学派为例)提出怎样的质询,以至当中可能触及何种哲学议题。”
所谓“朱子对‘是非之心’的特殊见解”,拙文提出两点:第一,在朱子,“是非”与“恻隐”“羞恶”“辞让”不同,本身可能不是一种道德情感。“我们或许会由于朱子以‘情’概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太快地以为此四者皆一概属于‘情感’(emotion)。”但拙文试图指出:在朱子的用法里,“情”不必皆指“情感”,而且“在朱子的论述里,‘是非’跟‘恻隐’‘羞恶’‘辞让’有着明显差异,其情感性格并不突出,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反而,当他描绘‘是非之心’时,却处处强调其‘分别是非’的认知或判断作用”。第二,此“分别是非”之功能,还只是一个比较表层或宽松的提法,更准确地说:“依朱子,‘是非之心’的真正重要的作用,是‘识是非之所以然’”,即“识别是之所以为是或非之所以为非的理据”。简言之,朱子的“是非之心”更应当被理解为“识是非之所以然”的作用,而非一种道德情感。
拙文第二部分进而讨论:“当我们掌握了朱子的‘是非之心’的上述特性后,我们在理解朱子在某些哲学议题上的立场和论证会得到什么帮助?”笔者于是以工夫论议题为例,探讨朱子对湖湘学派的“识心”工夫的反驳,并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朱子与湖湘学派的切磋,带入情感哲学(philosophy of emo-tion)的领域里。”换言之,准确掌握朱子“是非之心”的特性,对于深化宋明理学内部的哲学讨论,以及将这些讨论带入普遍哲学议题里,实有明显的帮助。是故,拙文总结道:“我们对‘是非之心’在朱子哲学中的特殊性(情感性格不明显、以‘识是非之所以然’即‘理由探问与提供’为其根本功能)应予注视,因为这样做将会更深入地理解朱子在某些哲学议题上(例如工夫论)的立场、思路和论证,甚至可以做出朱子所可说而未说的理论推演(例如有关‘识心说’的争议),以及测定朱子哲学所可能涉及的普遍哲学课题(例如情感哲学)。”
(4)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李瑞全教授发表了《朱子论心体的纠结历程:朱子早期之工夫论奋斗》。该文从北宋儒学的工夫论谈起,作为朱子于工夫体悟上之纠结历程的背景,一路谈到朱子从学于李侗(延平),却又不能接上其师的经过。全文辨析精微,尤其对《延平答问》里朱子与李侗之间种种往来讨论有极仔细的剖示,清楚阐明朱子如何曲折地走入理学语境、终又接不上程颢至李侗一脉之情形。
文中有两点特别令笔者受到启发。首先是作者认为“朱子之困扰实因成圣工夫自明道之兴发之后,实蕴含了一内在的实践上的循环(practical circle)”。其后,作者更进一步将此“循环”具体定性为“工夫实践之循环”(practicalcultivation circle)。宋代理学自程颢(明道)开始,工夫论(修养方法之理论)议题逐渐明朗起来。明道重在点出圣人境界,提示出一基本的工夫方向。其弟程颐(伊川)则更着手于具体工夫操作之开发,从而提出以“敬”涵养“未发”之一路工夫。然而作者本乎唐君毅之见,指出此路工夫实有一种困难:心体未发之时,一无所显,故无所谓“涵养”——要涵养也不知涵养什么,以其未显任何活动故;可是,“涵养”之工作一旦发动,则又已然进入“已发”状态。这就显出一种永在追逐而其目标——未发——又永不可即的“循环”况味。作者的见解虽说本乎唐君毅,唯其首倡“循环”一词以描绘个中情状,亦确然为前人的观点做了精到的概括。
其次,正如刚才提到的,李教授一文对朱子与李侗之间种种往来讨论有极仔细的剖析,清楚揭示了两师徒间隐微的义理分歧,这里稍举一例。对于朱子与李侗就孟子论“夜气”一章的讨论,李教授先言简意赅地点出:“延平教以持守此平旦之气,即是持守孟子之本心。”继而分析道:“孟子虽说有放心之时,但本心并不真是丧失掉,实只是此心被遗忘,被物欲所掩盖,宛若不见而已。由上可见,延平所教是持守此本心,涵养即涵养此心,而非如朱子引用伊川之以持敬致知的方式去涵养心体。由此可见,朱子此时实未能了悟二程之学,常有此种执实语句文义而不通透的论述,故延平亦常戒以如实平观前贤之说,不宜妄为比附之言。”如此细腻的剖析,让读者对朱子如何跟其师李侗,甚至程颢学脉最终分道扬镳,有一扼要的认识。
(5)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杨祖汉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
笔者观察所得,近年汉语学界(尤其香港、台湾地区)从事朱子哲学研究者大多以牟宗三的朱子诠释作为参照坐标,不论赞成还是反对牟说皆然。在此共同背景下,研究者所走的方向约有两种:或致力在牟氏诠释以外,另立一套更为妥善的朱子诠释;或大体接受牟氏诠释,而在牟氏之个别论断上提出异说或修正。前文介绍的郑宗义教授和以下即将介绍的杨祖汉教授,便恰好分别走了上述两条路。
杨教授近几年发表的朱子哲学论文,均在牟氏诠释的基础上,对牟氏之各种关于朱子哲学的评断予以再思。就是说,对于牟氏的很多主要诠释,例如“心性情三分”“心不即是理”等,杨教授均大体接受;而对牟氏的很多论断,例如“朱子之‘心’不能提供充分的道德实践动力”等,则进行重检。此次会议,杨教授即针对“道德实践动力”一课题,借助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之论尊敬,来揭发朱子“敬”论中的深层意蕴,试图论证朱子之“敬”论亦能在心学路数(主张“心即理”)以外对道德实践动力提供一种站得住脚的说明。全文结构与思理严整,推论步骤稳健。杨教授兼擅儒家与康德哲学,讨论起来自然出入无碍、左右逢源。
该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步骤,可借文中三段文字概括表述。首先,“朱子不主张‘心即理’这是很确定的,但心不即理并不表示理不能本在心中,吾人可以在心即理与心是气的区分外,说心虽不即是理,但心亦非只是气;即虽说心不是理,但心中有理,心本知理。即表示在人的现实经验的心灵主体中,虽然心不是理,但也不能说心对于理完全无知”。其次,所谓“心本知理”,此“理”即指“道德法则”而言,于是:“(……)了解什么是道德法则,就会承认法则对于意志能够直接地决定,而可以单因为法则的缘故而行,不为任何其他的动机(……)。要求人要无条件地只因为理的缘故而行,这种要求当然就是一种实践的动力。这是由认识到纯理而产生的动力,这一种动力可以只因为对于理的认识而产生,不必如牟先生所说,本心呈现才可以给出实践的动力。”最后,“以上运用康德论尊敬之意,阐释朱子也可以有因明理而生敬,因面对道德之理感受到理的庄严而又觉得自己现实生命不如理之纯粹,于是产生戒慎恐惧之情,从此一角度来看朱子的敬论,应该不算比附”。
(6)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劳悦强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以表证里——漆雕开与朱子的道德诠释学》。劳教授以其一贯敏锐的文字触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论语·公冶长》‘漆雕开章’,其中漆雕开回答夫子曰:‘吾斯之未能信。’原文并未直言‘斯’字的指谓,朱注则曰‘指此理而言’而并未提供训诂证据。再者,本章简短,才十六字,所记有限,而《论语》全书又仅此一章言及漆雕开,文献似不足征,然则朱熹如何诠释此章,从而洞悉漆雕开的道德修养境界,实在值得深究。”文章旨在剖析朱子“以表证里”的诠释手段及其所凭借的格物致知立场,务求通过朱子这位理学集大成者,展示理学本身的经典诠释风格。
该文首先借汉儒旧说,厘定“漆雕开章”的本意。劳教授说:“漆雕开所未能信者并非出仕时机是否适当,或应否出仕,甚至也非他对出仕之道尚有未明之处;他未能信者乃他本人的学问和本领。汉孔安国认为,漆雕开之所以未能信者,因为他‘未能究习’仕进之道,可谓切中原文意指。”接着,劳教授通过阐述张载与二程对此章的诠释,以表明朱注的理学渊源和基础。然后,文章便正式进入朱注之剖析。劳教授扼要道出了朱子的诠释原则:“原则上,朱熹解读《论语》文字就是结合外在讲究与内在经验的道德诠释,一方面强调实证的文本细读和入微的义理剖析,另一方面又玩味体认义理的主体之内在存养功夫及其气象。”简言之,对朱子来说,诠释经典,既要观言(细读经典文字),也要观人(玩味体认言说者的气象)。劳教授更从《朱子语类》卷二十九中拈出朱子“以表证里”四字,作为这种诠释风格的概括性表述。所谓“以表证里”,就是从言说者的外在表现(语言、行动等)证知其内里的整体人格和修养,从一事而见其全体。
然而,文本的“表”是有目共睹的,但要如何才能穿透文字的“表”,通达文本之“里”?这就得靠诠释者本人经过格物致知而得出结论了:能格物致知者,自能对“斯理”有深刻的体认,继而能以“斯理”去测定文本之“里”。但反过来说,阅读经典亦正是磨炼吾人明了“斯理”的途径,而为格物致知之一端。是故,劳教授在文末总结道:“解读文本自然不是一个道德行为,而且文本的内容也不一定与道德有关,但对朱熹而言,解读文本是一个格物穷理致知的活动,而所谓‘理’则寓藏于客观事物之中,因此归根究底,文本诠释自然以‘理’作为终极的义理参照。(……)一旦文本涉及人事上之‘斯理’以及其所有相关节目,朱熹便极力讲究读者与文本之间在‘斯理’上之默会体察,因为经典所载就是圣贤体验‘斯理’的记录。(……)因此,读书并非纯粹的所谓客观认知活动,而更重要的是读者借助书册上的文字,与圣人以心印心,从而体验‘斯理’。”
以上评述了会上六位香港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和观点。虽然当中只有(1)(2)(3)三位在香港任事,但广义而言,(4)(5)(6)三位亦可算入“香港朱子学研究者”之中。总括来说,在香港,朱子学的研究风气相对其他地区来说不算盛行,但其研究的路径却颇为多样:有对朱子文字做微观细析者,如(2)(6),有对朱子本人的思想进展做追踪描绘者,如(4),有对不同的朱子哲学诠释做比论者,如(1),也有致力将朱子哲学带入普遍哲学议题之讨论或比较哲学之视野者,如(3)(5)。可见人数虽少,却颇具活力;今后通过持续与其他地区学者的交流互动,可望不断推进香港朱子学研究的成绩。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2013—2014年美国朱子学研究综述
戚轩铭 刘倩
在2013至2014两年间,美国有关朱子学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发展。虽然相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其著作、文章的数量并非蔚为大观,但其研究质量与成果值得学界了解和重视。本文即为一篇按专著、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这一顺序对近期美国朱子学研究情况加以介绍的文献综述。[1]
学者艾周思(Joseph A.Adler)于2014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Dao:ZhuXi’s AppropriationofZhou Dunyi)是一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专著。[2]学界长久以来多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朱子的思想,然而,艾周思在这部专著中却从宗教实践的角度详细讨论了朱熹如何运用周敦颐的思想来进一步发展儒学。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于上述观点议题的讨论分析,第二部分则主要是对重要文献的翻译。
在第一部分中,艾周思一方面探讨了周敦颐在朱熹的道学谱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也细致讨论了朱熹如何运用周敦颐的思想,并解释了周敦颐思想当中某些概念的意思。艾周思首先描述了朱熹所建构的道统,认为根据朱熹的观点,这个道统在孟子之后便中断了超过一千年,而接续这个道统者应为北宋之周敦颐而非后来的二程。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朱熹认为周敦颐和伏羲一样,在没有任何人的指导下便能全面地理解“道”。不过,艾周思也同时指出,朱熹视周敦颐为圣人之道的接续者,这种观点在宗教、哲学和历史三个方面都造成了若干问题。在肯定了周敦颐在朱熹所构筑的道统之中的地位后,艾周思继而讨论了朱熹如何利用周敦颐“动静互通”的思想来作为其自我修养的方法的基础,借此处理他在1160年所面对的思想危机。此外,周敦颐最重要的思想为“太极”,艾周思在最后主张应以“Supreme Polarity”而非“SupremeUltimate”来翻译“太极”一词。他解释这样翻译的原因,是因为“太极”虽是一个终结,但同时亦是一个转折,故“Polarity”能更好地表达这重意思。而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艾周思则翻译了周敦颐一些最为重要的著作,朱熹对于这些著作所做的注释以及朱子和其门生对于这些著作所做的讨论。
除了艾周思有关朱子学的专著以外,贾德讷(Daniel K.Gardner)在撰写《儒学简介》(Confucianism:A Very Shortlntroduction)这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的著作时亦用了一章的篇幅简单介绍了朱熹的学说。[3]作者认为朱熹或许是当时众多理学家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并分别描述了他有关“理”与“气”的形而上哲学,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自我修养功夫、步骤和方法等。
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学者也发表了若干讨论朱子学的论文。田浩为当今美国朱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自2012年其著作《旁观朱子学》出版以后,他撰写了多篇论文继续探讨朱子学当中的议题。首先是他与现为普渡大学助理教授的女儿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共同撰写的《儒家婚礼之重构与现今中国青年文化:援引经典以回应棘手问题的案例》一文。[4]朱杰人和张祥龙这两位复古派学者为了提倡并恢复传统仪式与文化,故各自为其儿子策划并举办了儒家婚礼。而此文则深入分析了这两场婚礼的社会意义,以及两位学者如何将现代元素融入两场婚礼之中。同时,它亦探讨了两场婚礼的具体差别。为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两位作者还特意访谈了参与者,论述了其他学者对这两场婚礼的评价。在文章中,他们认为从恢复古礼以及让参与者明白古礼的价值方面来看,两场婚礼都是相当成功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2年,田浩与田梅就此议题,还共同合作撰写了《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一文。这两篇文章无疑都是对儒家婚礼与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积极探讨。
同时,他亦曾与殷慧合著《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一文。[5]该文从礼理的关系讨论了宋代经典转型的问题。两人指出“五经”和“四书”都是以“礼”为中心的,但后者对于“礼”的发挥则比前者更为集中,且更关注于“宇宙论”及“心性论”,故此宋代之理学家渐渐以“四书”取代“五经”。而在这过程中,这些理学家,如朱熹等并没有如清人所言般以理代礼,而是认为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即前者是后者的精神内涵。此外,田浩还撰写了《郝经对<五经>、<中庸>和道统的反思》一文。[6]本文虽未直接讨论朱子思想,但它却讨论了学者郝经如何继承和变更朱熹的思想。田浩在该文中指出,在1255年之前,郝经基本上是接受朱熹对于道统的理解的。他虽然对“五经”的看法与朱熹的观点有同有异,但他在后来还是接受了朱熹对于“四书”,特别是《中庸》的观点。但在1255年之后,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郝经改变了过去对于道统的理解。
最后,《<朱子家训>之历史研究》一文则简要地回顾了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世界朱氏联合会有关《朱子家训》研究的发展情况。[7]他将这段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认为《朱子家训》是家庭道德的标准。而到2002年,五位政府官员所发表的论文则显示它是来自封建社会,却依然对社会主义道德标准颇有补益的典型中国价值观。而2010年于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会议中,学者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中国对世界普世价值的重要贡献,应予以推广。
除了田浩以外,以下两位学者亦曾发表论文讨论朱熹的思想。首先,庞安安(Ann A.Pang-White)《朱熹的家庭与妇女观:挑战与机遇》(ZhuXionFamilyandWomen: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一文通过比较朱熹的两类文献考察了朱熹的妇女观。[8]她指出从现实的层面而言,朱熹对于女性的态度是颇有弹性和开明的。其次,朱熹有关阴阳与男女关系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最后,庞教授认为朱熹对于女性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的观点是带有进步性的,并指出这种进步性或源于朱熹形而上思想的稳步发展。
其次,白诗朗(John Berthrong)的论文名为《荀子与朱熹》(XunziandZhuxi)。[9]他撰写这篇论文是为了证明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思路接近荀子而非孟子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及重要性。他在该文中比较了荀子和朱子对于“理”和“心”的理解。白诗朗认为在朱子的体系中,“理”既可作Coherence或PattemmOrder,亦可作Principle。其原因在于,朱子赋予了“理”一个道德内涵。就“心”而言,白诗朗指出朱子对于“心”的理解大致有两点。首先,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或“心妙性情之德”。其次,朱子认为“心”在概念上是单一的,而不是相对的。
另外,在去年10月初,亚洲研究学会美西(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Western Branch)研讨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田浩在会上还主持了一场主题名为“重读朱熹与道学:宋元时期之儒学”的报告会。会议报告者皆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报告的论文题目包括:张晓宇:《转向内在的道:北宋晚期新学派“道学”一词用法之考察》;吴思远:《论朱熹对苏轼的一些看法》;张琎:《大儒之友道:对吕祖谦与朱熹交往的反思》;刘丽丹:《论中韩文化交流中白云洞书院对白鹿洞书院的接受》;温佐廷:《为古道辩护:元好问对道学态度之考察》等等。
就学位论文而言,当中虽无专谈朱熹或朱子学者,然仍有两篇博士论文约略讨论了朱熹的华夷观和他关于“命”的看法。前者为杨劭允(Shao-yunYang)所撰写的《重塑蛮族:中华帝国中期(600—1300)对夷狄在修辞及哲学上的运用》(Reinuentingthe Barbarian:Rhetoricaland Philosophical Uses ooftheYi-Di in Mid-Imperial China,(600-1300))。[10]而后者则是由白英宣(Youngsun Back)所撰写之,《掌握命运:儒家对命的论述》(Handling Fate:TheRu Dis-course on Ming)。[11]杨劭允的论文探讨了唐代至元代学者华夷观的演变。杨劭允在论文的第八章中依次讨论了朱熹等道学家是如何理解华夷之间的区别的。他指出朱熹认为人与夷狄是截然不同的,而只有中国人才算是真正的人。其次,杨劭允指出朱熹并没有明确地通过“理”和“气”的概念来解释人和夷狄的不同。因他的学术旨趣并不在此,而且朱熹也意识到这种做法有一定难度。同时,杨劭允又认为朱熹对于华夷的态度既与其他道学家有异,亦使其道德哲学表现出种族优越的特色。
白英宣的论文以纵向的方式探讨了“命”这个概念的演变。在该文的第二部分中,白英宣比较了朱熹和丁若镛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她首先指出朱熹学说的宗旨是希望人们能实践成为圣人的方法,而她在论证过程中亦提到朱熹认为“天”与“理”的意思是相同的。随后,她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朱熹有关天命、立命和正命的问题。她指出,在朱熹眼中,“命”与“理”和“气”是有关联的。又据她所言,朱熹认为只要人们能实践成为圣人的方法,那么他们便可得到正确的“命”,反之亦然。
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
〔韩〕姜真硕
2014年韩国的朱子学研究大概可区分为五种领域。从研究范围看,分别有关于“四书”或“五经”的朱子注释书的研究,关于朱子学与宋代儒学的研究,宋儒文献或《朱子文集》传播于朝鲜的研究,朝鲜朱子学的话语及其内容之研究,关于李退溪、李栗谷、丁若镛等朝鲜大儒的研究。其中,笔者把值得给读者介绍的论文按照几种研究领域区分如下。
第一,关于“四书”或“五经”的朱子注释书的研究。
Min Hyoung-hee:《<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历史学研究》53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一方面介绍《四书章句集注》给南宋士大夫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朱熹对“五经”和“四书”的见解。作者认为朱熹似乎把“五经”看作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五经”类的文化产物中难以找出基于道统的道德规范。为了帮助学生寻求内心的道德规范,朱熹选择了既更具整合体系又更善于提出他的思想体系的四种文献,即“四书”。为了把文化传统与他的形上学体系成功地结合,朱熹重新定义了儒家的文化伦理传统,并把天地概念注入其中。
Kim Do-il:《在朱子对<大学>的解释中的实践问题——“止于至善”为何是独立的纲领?》,《退溪学报》136卷,2014。
作者强调“止于至善”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完成。换言之,“止于至善”之实现,是道德修养的人从“明明德”出发,扩充为“新民”,在更为扩大的共同体中不断实践后才能完成的。
陈礼淑:《孔子诗经观与其后学的反响——以朱子与其后学为主》,《汉文学论集》39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详细介绍了朱熹对孔子删诗说的看法有时期的区分。早期朱熹相当接受孔子删诗说,承认孔子“去其重复,正其纷乱”的积极角色。之后,因受到彻底不信且批判诗序说的郑樵的影响,朱熹放弃诗序说,修正孔子的删诗说。后期,朱熹进一步认为孔子只言郑声淫乱,而无言删去诗,因此“孔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由此可见,朱熹前期和后期的诗观,有删诗说与刊定说之区分。
第二,朱子学和宋代儒学的研究。
Hong Sung-Min:《在朱子的伦理学中的差等对待的正当性》,《中国学论丛》43卷,2014。
作者在分析朱子“参赞化育”思想的过程中指出朱子以诚之态度把我们的关心和关怀扩大为整个万物之生命,这些学说可成为朱子哲学之生态伦理的理论根据。天地的生命意志与人的伦理实践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由此可找出等同又差等的逻辑之可能性。基于这些内容,我们可确认朱子生命伦理的差等对待是与“各得其所”息息相关的。
Boo Ji-hoon:《张载的大心工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以格物致知为主》,《东洋哲学研究》78卷,2014。
作者认为朱熹对于张载的大心工夫以扩充知识方面始终保留怀疑的态度。如果没有格物穷理的支持,仅仅做大心工夫只不过是空虚地扩充内心。朱熹解释格物致知时强调见闻知,他一方面接受张载提出的见闻知与德性知的两层结构,另一方面弄清此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树立自己的哲学。在朱子哲学里,见闻知被看成外在知识的所得,而德性知被用于内在修养之完成。
Shin Chun-Ho:《德治的目的和难点——关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论争的考察》,《韩国道德教育学会》年次学术大会,2014。
作者说明陈亮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要排斥道和义的道理。他强调的是在实际统治的现实中不能忽视义和利的两面,应该同时考虑此二者才能实现完善的统治。作者进一步认为,陈亮提出周公的统治例子成功地反映了他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由此看来,陈亮认为,朱熹提出的德治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出实际效应,应当依法实行赏罚制度。
第三,宋儒文献或《朱子文集》传播于朝鲜的研究。
Song ll-Gi:《永乐内府刻本<四书大全>的朝鲜传来与流布》,《韩国文献情报学会志》48卷,2014。
作者介绍了明代中国编纂的《四书大全》,世宗一年(1419)首次传播于朝鲜。世宗八年(1426)和世宗十五年(1433)再传至朝鲜。世宗八年(1426),世宗命令庆尚监司刻印《性理大全》《五经大全》。朝鲜时代刊行的《四书大全》集中刊行于庆尚道和京畿道等地区,而且集中刊行于18世纪即壬辰倭乱。清朝顾炎武等学者严厉批判《大全》本的刊行时,朝鲜境内《大全》的刊行反而最热,显示了当时两国学术风气之不同。
Lee Young-Ho:《朝鲜的朱子文集的注释书及其意义》,《大同文化研究》88卷,2014。
作者介绍了朝鲜学者对朱子文献的注释及其演变,认为朝鲜时期最早的注书是对李退溪《朱子书节要》一书当时和后代的注书。宋时烈注释《朱子文集》,完成了《朱子大全箚疑》,宋时烈的弟子们在之后的二百年间进行了修改。经历了这些工作,李恒老等学者终于完成了《朱子大全箚疑辑补》。朝鲜朱子学的朱子学文献的注释面貌可谓从宋时烈的《朱子大全箚疑》出发,到《朱子大全箚疑辑补》完成。
第四,朝鲜朱子学的话语和其内容之研究。
Kim Baeg-hee:《朝鲜前期儒学的伦理主体性的形成与变换——以郑道传和李退溪为主》,《东西哲学研究》74卷,2014。
作者介绍了朝鲜时代的代表人物。郑道传是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李退溪则是在朝鲜中期士祸不停之际重新解释朱子学的儒者。作者认为郑道传构想的伦理主体是奉献于建设共同体的朱子学之人。他们认同社会一体化的理念,是为社会全体做贡献的集体智慧之一员。相对地,在守成期活动的李退溪所构想的伦理主体则是以朱子学的理念为自我认同,把道德价值能动地实现于社会的人。因此李退溪特别强调理发之能动性。
Kwon Oh-young:《朝鲜朱子学的理学话语及其特色》,《朝鲜时代史学报》69卷,2014。
作者认为朝鲜朱子学重视穷理,更重视敬的修养。李退溪建立朝鲜朱子学的体系时,提出敬为核心概念。以退溪学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归结于敬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周世鹏建立白云洞书院时把敬字刻在河上岩石。李退溪继承这些朝鲜的敬传统,又传承真德秀的《心经》传统,提出朝鲜儒学的敬哲学。
Kim Woo-hyung:《金昌协的知觉论与退栗折中论的研究——知觉与智的分离所产生的道德心理学的见解》,《韩国哲学论集》40卷,2014。
金昌协是在朝鲜时代人性、物性同异论争时期活动的儒者。作者从李退溪和李栗谷思想的折中意义上来探讨金昌协的知觉论。金昌协继承了宋时烈重新树立朱子学的时代意识,把退溪学和栗谷学的综合作为自己的时代课题。为了说明这些内容,他试图把心知与智知作为整合的范畴而发挥他的思想。金昌协在心论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宋时烈的思想,而由此进一步发挥知觉是兼心之体用的学说。他的退栗折中论可说是把“理乘”义引申为如李退溪把理发义看成内在于善之本性的道德原理。
第五,朝鲜大儒的研究。
Jeong Sang-bong:《茶山的人们观与孝悌慈的实践》,《韩国哲学论集》43卷,2014。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从伦理学的角度重新探讨丁若镛的哲学思想。作者认为,在丁茶山的思想中,人兼备身体倾向与精神倾向。其中,特别是好善恶恶可说是人的本质,是上帝之天赋予人的。人具有自律的判断能力和具有主体之实践意志的自主之权。人虽然有向善之倾向,但是具有自律又主体特色之人的行为是有善有恶的。上帝随时随地监察人的动机和行为的善恶与否。上帝之声是从人的道心中响彻出来的。这就是伦理实践的外在动因,也是内在动因。
Kim En-zhong:《丁茶山对朱子<论语集注>的批判(七)》,《汉字汉文教育》33卷,2014。
这篇论文是作者关于丁若镛对朱子学的批判方面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介绍了丁若镛否定仁之内心说,而主张人心具有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理发现于外而在行事中实现的是仁义礼智。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归”的解释方面,朱熹说:“归,犹与也。”丁若镛解释“归”为归化义。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解释方面,作者认为朱熹把足食和足兵看成民信的一种先决条件,茶山则认为三者各为一事,不一定互相有关系。在“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解释方面,朱熹比较重视君主与百姓的上下关系,茶山认为君主与百姓皆是以信任为基础,在同等关系上互相作用的。
以上大概介绍了2014年韩国朱子学研究的内容。各领域的研究分别显示朱子学、朱子文献学、朱子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朝鲜朱子学对南宋朱子学的继承和修正、其他朝鲜大儒的哲学等内容及其特色。除了笔者在这里介绍的论文之外,韩国学者每年都认真地研究退溪学、栗谷学、茶山学等韩国儒学的三大领域。不过,在2014年的研究成果中,我们难以找到传承韩国朱子学或解释朝鲜儒学而提出的一些应用哲学或现代伦理学方面的论文。
(作者单位: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2013—2014年韩国栗谷学研究综述
赵甜甜
韩国对朱子学的传承和发展在儒学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由于朱子学是朝鲜王朝建国的理念,而儒学知识阶层的掌权更是使朱子学在韩国逐渐本土化,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使朱子学不仅仅在理论层面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更深入到实践之中,渗入到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栗谷李珥在朱子理论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韩国朱子学进行研究时,栗谷思想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
此篇综述的数据是基于韩国三大论文检测网站“RISS·KISS·DBpia”上的结果,可能会有不详尽之处,请各位学者大家指正。
2013—2014年关于栗谷思想研究的单行本有24本,其中李光虎所著的《退溪与栗谷,思想的花火》一书,通过分析退溪和栗谷之间往来的书信,找出二人思想的碰撞点,使读者不仅能看到两位韩国大儒的思想花火,还可以体会到学术交流的乐趣。作者李光虎四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学真理,并努力从现代人文学的角度上重新阐释经典,本书有史以来第一次汇编了二位大儒往来的书信及诗文,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二人在学术上各自所坚持的信念。退溪的理论体系非常重视理想世界和人类的内在世界,而栗谷的理论体系则更加重视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外在世界,二人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讨论。读者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二人的思想,更可以从中获得许多人生的智慧。
《儿童击蒙要诀》则以栗谷最著名的《击蒙要诀》为基础,从立志、革旧习、持身、读书、事亲、丧制、祭礼、居家、待人、处世这几个方面,简单明了地向初学入门的孩子们介绍了为什么要学习,如何学习,要学习什么,以及如何为人处事等等。《击蒙要诀》是栗谷为了启蒙儿童和初学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对于学生来说是一本可以受用一生的著作,译者(HAN MUN HI)在忠于原著的同时,以更加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解释方法进行了阐释,对初学儿童的教育极具意义。
《栗谷李珥评传——朝鲜中期最优秀的经国大家·伟大的导师》一书是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永愚的新作,此书从栗谷的家庭入手,对其母亲申师任堂的子女教育进行了肯定,对栗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和思想,并认为栗谷是社会思想改革的先驱,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是不容忽视的。
2013—2014年间有关栗谷思想的学术论文共有77篇,大部分论文是对栗谷思想或栗谷学派思想的研究,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不乏比较研究和跨领域交叉研究。比如金世贞在《율곡학을 통해 본 인간과자연의소통과공생의해법》(《从栗谷学中寻找人与自然交流和共存的解决方案》)一文中,分析了西方生态学的特征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对栗谷学中的生态理论,以及其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寻找出栗谷学中人与自然的交汇点。栗谷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在参与天地化育的过程中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实理以实心的形态内在于人类,通过诚实心可以与实理统一,亦即人类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起到了克制的作用,也将成为人与自然共存与沟通的思想基础。
俞成善则在《中国的栗谷学研究现况及成果研究》中指出栗谷及栗谷学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现阶段对韩国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理学的研究上,其中又以退溪学与栗谷学为主。中国学界对退溪学和栗谷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中韩国际学术会议的开展,与中国国内韩国研究所的合作,对韩国哲学研究的深化和扩大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作者站在东亚思想的角度上,客观地评价了栗谷学研究的意义所在,认为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和栗谷学研究急需培养专门性的人才。
《‘실천학’‘으로서의’실학' 개념 : 율곡 개혁론의 철학적 기초:》(《作为“实践学”的“实学”概念:栗谷改革论的哲学基础》)一文以历史学界在过去80年对“近代实学观”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分析“实学”的概念。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文章从栗谷“实心”的概念出发,对栗谷学中从“实理”到“实心”,从“实心”到“实政”,从“实政”到“实行”的“实心实学”概念进行再解释,认为这种积极强调践行的“实践学”思想植根于栗谷的改革论之中,并形成了茶山丁若镛的“行事”概念和东学的“学”概念。
相比较而言,近两年关于栗谷思想研究的学位论文较少,共计有12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只有2篇,硕士论文10篇。这些硕士论文选题新颖,摆脱了传统思路,试图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解释栗谷思想,如:《퇴계와율곡의 성 리학 사상으로 본공간조형개념 비교 연구》(《退溪和栗谷的性理学思想与空间造型概念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退溪和栗谷的性理学思想在韩国传统建筑的空间造型艺术中有很多体现。例如,天地秩序体系中的谦虚与恭敬思想体现在空间的大小、构成、布局和位阶、秩序上,而建筑正南向的布置,明确的区域功能划分及空间的开放性则是礼思想的体现,建筑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则体现了天地和合的思想。
徐明子在《栗谷의孝思想研究:“圣学辑要”‘孝敬章’을中心으로》(《栗谷孝思想的研究:以<圣学辑要·孝敬章>为中心》)一文中,从“孝敬”入手,分析孝敬的重要性,找出孝敬理气论的根据,认为以孝守身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文中强调这种孝并不是愚孝,而是可以谏言的孝,孝的方法则可以分为“生事之道”“丧礼之道”“祭礼之道”。
《栗谷의 저술에 나타난자녀교육관 연구》(《对栗谷著作中出现的子女教育观的研究》)中以子女教育作为切入点,系统地考察整理了栗谷著述《同居戒辞》《击蒙要诀·事亲章》《击蒙要诀·居家章》《圣学辑要·正家篇》以及《小儿须知》中所体现的子女教育思想,认为其榜样教育、适时习惯化教育、知行并进教育以及理性对话的训诫教育不仅在朝鲜时代,而且对现代的子女教育也十分具有典范作用。
2013—2014年关于栗谷思想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会议莫过于2014年10月31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600周年纪念馆隆重召开的主题为“东亚朱子学与栗谷学的位相”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韩国栗谷学会与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BK21事业团共同主办,同时得到了栗谷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栗谷学会会长崔英辰希望东亚各国都能以“朱子学”为核心,跳出“一国史”的观点,从“东亚史”的层面上寻找各国儒学的同异,摸索出现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来自法国、日本、中国的知名学者以及极具潜力的新晋学者们做了精彩的发言,为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研究和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其中孙兴彻在《栗谷理通气局说的内包和外延》一文中考察了栗谷理通气局说的发展和变化,而李向俊则在《理,事物,事件——李珥的情境》中活用西方最新的分类学学术成果,结合栗谷理气心性论的构造进行探索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在论文集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2013年年底“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的结集出版。“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2012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成功召开,由于此次会议跨越了多个学科、多个领域和多个地区,有27个议题,69个场次,所以其论文集的出版显得难能可贵。收录在《东亚视域中的儒学:传统的诠释》一册中的论文有多篇涉及了栗谷思想,尤其是崔英辰《19—20世纪朝鲜性理学“心即理”与“心即气”的冲突:以艮斋和重斋对寒洲“心即理说”的论辩为中心》一文中,系统整理了退溪和栗谷学派对于心、性、理的看法,而栗谷思想对于后代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影响深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栗谷所编撰的《击蒙要诀》现在仍作为中小学生必读书,其所产生的教育意义在现代社会仍不可估量;而其母亲申师任堂也作为现代社会女性的典范,不断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因此可以说栗谷思想中所承载的孝思想和教育思想至今传承不息。
对于栗谷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韩国国内,中国也开展了相对活泼的研究活动。大陆学者除了陈来、李甦平、潘畅和,还有很多年轻学者,例如邢丽菊、洪军等。而中国台湾对韩国儒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栗谷学方面的专家,在此不一一赘述。
(作者单位:韩国成均馆大学校)
2014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日〕板东洋介林松涛译
1.现代日本思想界关注儒教——《现代思想》儒教专辑
《现代思想》杂志2014年3月期(青土社)推出了一个专辑,题为《当今为何谈儒教?》。日方作者有:安富步、土田健次郎、中岛隆博、石井刚、泽井启一、吾妻重二、井上厚史、伊东贵之、羽根次郎、本间次彦、马场智一(按撰稿排序)。中方作者有:张志强、谭仁岸。此外还收有两篇对谈——当代日本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与文艺评论家、台湾史专家丸川哲史之对谈,以及载于《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清华大学,2010年10月)的齐泽克(S.Zizek)、鲁策(A.Lusso)、海裔、汪晖四人谈的日文译文。代表了当今日本水准的儒教研究者及评论家群英荟萃,蔚为壮观。《现代思想》是一份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思想性杂志。每期“专辑”介绍一些欧美著名的思想家、欧美社会与政治思想、日本国内与国外的时事问题等,其选题反映出日本知识阶层的关心所在之推移,本期《当今为何谈儒教?》这一标题在其中独放异彩。在2014年的日本,《当今为何谈儒教?》——这当然既不是挖掘业已过时、化为“知识化石”的思想,也不是如在博物馆眺望陈列品。无非因为中国大陆对2014年的日本而言,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领域获得了对昔日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影响力,几乎成为最巨大、最重要的“他者”。然而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共同体的决策架构,对外部的人来说还是雾里看花。因而,当今的日本人自然地将强烈的关心投向曾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整合之原理,近年来随处听到“复兴”呼声的思想上与礼制上的传统——儒教。其中存在着希望理解他者的迫切愿望。
本期杂志的撰稿人大半或含蓄或明确地表明了上述及其当下的问题意识,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日本学者共同拥有的态度。例如,谭仁岸与张志强分别介绍了在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叶的中国“传统”儒教的复兴过程,文中仿佛渗透出在传统儒教与近代乃至共产主义之间激烈摇摆的当代中国的热气沸腾(《传统现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中国)》、《儒学の“创造的转化”(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与此相对,日本作者较多作为主题的则是,如何自我反思潜在于以往的日本人的儒教观之下的意识形态。例如,泽井启一批评了以往的日本儒教研究中存在的“仅关心儒教‘日本化’的日本中心主义”倾向,相反将以往被视为儒教“日本化”的现象作为儒教本身内在的“本土化”运动之一环来反思(《土着化儒教日本(本土化的儒教与日本)》)。另外,井上厚史论述了井上哲次郎(1855—1944)与高桥亨(1878—1967)等战前帝国日本的儒教研究之泰斗们如何恣意地制作出停滞的朝鲜儒教与先进的日本儒教之对比构图(《封印朝鲜儒教(被封闭的朝鲜儒教)》)。此外,尤其是对引领了战后儒教研究的沟口雄三(1932—2010)的中国观,也进行了可谓相当严厉的反思(伊东、吾妻、本间论文)。这样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与其说是当今活生生的儒教,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迄今为止对儒教的态度构成了主题。究其缘故,一是由于日本不同于中国大陆,儒教不管是作为思想教说还是礼仪制度都未融入现代日本生活中,另一是由于日本受到了较之活生生的现实,更关心“话语”内部权力性的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互动。当然,往昔日本的儒教观中存在的“落后的大陆、进步的日本”这一价值意识,在当今仍很难说已被彻底根除,不断找出此类狭隘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日本人来讲,仍是当下迫切的问题。可是,“重新谈论儒教至今是如何被谈论的”这一态度,归根结底不得不说是在学术界内部“自我言及”性的,这是与在中国或在韩国一谈起“儒教”便会出现的属于这一社会的人无不关心的热气沸腾所无法比拟的。作者之一中岛隆博一方面关注试图通过复兴读经与释奠等来恢复地域社会之公共性的中国现状,一方面针对因反思战前压抑性的“国民道德”而造成的战后完全空白化的日本地域性公共空间,这样写道:“不妨摸索一种以不同于国民道德及‘教养’的方式来尝试参与公共领域的儒教之可能性。”(《儒教、近代、市民的 (儒教、近代、市民性灵性)》)大约在日本,通过在地域开展礼仪、实践来重塑“地方性、市民性的灵性”(上述中岛论文)真正起步时,作为“传统”来参考的不是儒教,而是佛教与神道,但中国的儒教传统之复兴同时也引出了在现代日本如何构想“家礼”与“乡礼”这一极为现实的问题。
2.山崎暗斋与朱子学的“本土化”——泽井启一《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
正如上节所述,贯穿于当今日本儒教研究背后的倾向变了,整个基调从寻求日本儒教的独自性,转向关注其与东亚儒教文化圈整体的联动性、互动性。这一倾向显著地表现在有关山崎暗斋(1618—1682)的研究、论著之增加上,耐人寻味。战后日本的近世儒教研究中以往最受瞩目的是全盘否定朱子学,树立起独自思想体系的荻生徂徕(1666—1728)。自丸山真男的划时代巨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以来,在徂徕思想中发现了日本独特的先驱性近代,以及日本儒教的独特性与先进性。然而,近年来仅专业性著作就出版了高岛元洋《山崎暗斋——日本朱子学垂加神道(山崎暗斋——日本朱子学与垂加神道)》(ぺりかん社,1992)、朴鸿圭《山崎暗斋の政治理念(山崎暗斋的政治理念)》(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田尻祐一郎《山崎暗斋の世界(山崎暗斋的世界)》(ぺりかん社,2006),今年又有泽井启一《山崎暗斋——天人唯一の妙、神明不思议の道(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ミネルヴァ书房,2014.3),暗斋研究凌驾于徂徕研究之上,呈现出一片欣荣。
近年暗斋研究之盛与暗斋本人在思想史上所占的极其微妙的地位相关。仰慕朱晦庵之名而自号“暗斋”的山崎嘉右卫门敬义在整个日本近世是一位最醇、最敏锐的朱子学者,他还尊信朝鲜大儒李退溪(1501—1570)。暗斋的思想与实践中重“敬”高于一切的想法被认为来自退溪的影响。可是暗斋同时也是一位倾心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试图合朱子学与神道为一体的人物。作为神道家暗斋自称“垂加”,他开辟的垂加神道在近世形成了最大的神道势力,同时对明治时代以后的国粹主义也施以了巨大影响。暗斋究竟是最纯粹的朱子学者,抑或是狂热的神道家、日本主义者?对此泽井启一甚至说:“暗斋的真面目是儒教抑或神道,以及该两者出于什么理由得以并存?”这一设问“或许可说是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最大的谜”。有学者认为,对于暗斋而言,神道是使朱子学根植于日本风土中的无可奈何的韬晦(朴鸿圭上述著作等),也有学者认为相反,对暗斋而言,朱子学只不过是他彻悟神道中蕴藏的日本固有精神的触媒而已(近藤启吾等人)。山崎暗斋这一思想家恰恰立足于赞赏日本之独特性的民族主义与朱子学这一前近代东亚的普遍性思想的分岔路上。研究中心从徂徕向暗斋转移极具象征意义。
作为今年“ミネルヴァ日本评传选”之一册出版的泽井启—《山崎暗斋——天人唯一之妙、神明不可思议之道》,如上所述明确了暗斋的特殊地位后,不局限于暗斋的思想,而对其出自、学统、门第、交游,乃至从政治、经济至出版状况的当时知识环境广加探讨,与以往的“较之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更关心)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成立的”这一研究趋势相反,勾勒出了“作为个人”的暗斋像。本书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对构成暗斋研究中的“最大的谜”并一直找不到答案的他接受神道问题,不是如以往那样从“日本固有性”这一文脉来把握,而是作为对朱子学重视的实践(“穷理”与“居敬”)进行“本土化”,即“改变为合于自分的时代与地域者”的一个环节来把握。泽井启一认为,暗斋之接受神道只是承继了源自宋代朱子等人的巨大思想潮流的,各地域、各时代的所有人物——如明代的王阳明与李氏朝鲜的实学者们,以及近世日本的古学者们——分别与自己的时代、地域相结合,对实践方法加以修正的尝试之一。泽井启一关注的是在暗斋生活的近世日本社会中儒教式礼制未扎根这一点。在近世日本社会,政府强制规定丧葬以佛教式进行,并且也未开展《小学》中体现的礼法之幼年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能与周围不产生矛盾而履行“敬”之形式,他发现了神道礼仪与实践。泽井启一得出的结论是“用神道这一‘本土’素材”“在日本使朱子学得以实践”才是暗斋根本的目标。这一理解当然是载于《现代思想》的论文《本土化的儒教与日本》中泽井启一本人所提示的见解的具体应用。不拘泥于日本的固有性,从“东亚”规模来把握日本儒学,这正是当今学界所共有的姿态,以这一姿态来具体地探究一位思想家,能够开辟出怎样的新视野?泽井启一的著作如此给出了一个范例。
3.奔波于东亚的朱子学者——《季刊日本思想史》朱舜水专辑
整个近世日本,水户藩(现在的茨城县)一方面作为德川的“御三家”之一,成为德川军事政权之重镇;而另一方面,好学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招请明朝遗臣朱舜水(1600—1682)开设彰考馆之后,也作为日本近世的儒学研究中心延续下来。“水户学”在近世儒学界一直占有独特的位置,直至近世末期,作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性动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参与维新的志士们无人不受“水户学”之影响。维新后,水户学相关资料之大半秘藏于水户德川家,其中包括众多与朱舜水有关的资料。近年来,这些资料移归公益财团法人德川博物馆保管。2010年台湾大学举办“朱舜水与东亚文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契机,2012年开始了为时三年的史料调查。由中、日的研究者参加的该项调查之结果作为《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I——朱舜水文献释解》(2013)、《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Ⅱ——德川光国文献释解》(2014)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东亚各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明年预计出版《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Ⅲ——水户藩的内外关系文献释解》。《季刊日本思想史》杂志第81期(2014.9)以“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之学问”为题,向学界公开了目前的部分研究成果。中、日学者基于新资料各自发表了探讨朱舜水及与德川光国相关问题的饶有趣味的论文。其中包括朱舜水来日前的活动、德川光国与朱舜水的相识、光国之思想形成、舜水带来的书画与夫子像之实际内容、安积澹泊(1656—1737)等舜水门弟们的思想,以及实际上如何接受舜水带到水户藩的思想中大约最重要的朱子学式礼法的情况等,弥足珍贵的一册著作让读者联想起以舜水与光国为中心的水户朱子学之概况。
其中受到关注的是,此次证实了以往的舜水研究中对是否实有其物争论不休的舜水所持南明鲁王之敕书,并在该杂志上登了照相版与翻刻。对2013年9月2日“发现”敕书时调查团成员的神情,杨儒宾做了如此描述:“九月二日,传说中的‘鲁王敕书’由博物馆员解开纽解,当我们看到朱舜水生前秘藏而不示与人的那封敕书时,调查团的成员都在静悄悄的馆内或感叹不已,或瞠目结舌,或热泪盈眶。……”(《异乡家乡——鲁王朱舜水の物语(异乡与家乡——鲁王与朱舜水的故事)》)
大约四百年前朱舜水所扬帆渡过的,正是今日化为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冲突之地的中国大陆东方、日本西南方之水域。迢迢万里来到远东之岛国,乃至更东方的水户之地,不改敬奉明之遗王态度的朱舜水之身姿,形象地向年轻有为的君主德川光国显示了对构成朱子学之核心的“理”之无穷的信仰究竟为何物,这促使德川光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当时日本尚且陌生的,作为舶来新思想的朱子学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来到日本之一瞬。据说放置舜水所秘藏的鲁王敕书的木匣,在幕末弘道馆之战中刻下深深的弹痕(德川真木《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关于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弘道馆之战发生在舜水去世一百八十年后的1868年,这是一场学习奉舜水为祖学的水户学的水户藩士们中的保守派为死守水户藩学馆弘道馆,与站在新政府一方的革新派交火,双方死伤惨重,并令弘道馆之大半与珍贵的典籍一同化为灰烬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战争。奔波于东亚的朱子学者舜水、与舜水有关的水户学者们虽然都是为了理而不辞行使武力之人,可是舜水亲身传至日本的朱子学之神髓不是向国外胡乱炫耀暴力等,而是不屈于任何逆于理的权势与暴力的英勇的自立姿态,面对这位对日本道学有大恩大德的先儒,今日仍需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作者单位:日本学术振兴会)
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综述
傅锡洪
朱子学初传日本是在朱子去世后不久的13世纪初期,不过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朱子学文献被淹没在浩瀚的佛教文献当中,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直到17世纪初期,日本结束战国时代,进入比较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江户时代(1603—1868)以后,由原本是僧人的藤原惺窝发其端,朱子学才开始兴盛起来,并且涌现出林罗山、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山崎暗斋、中村惕斋、贝原益轩和新井白石等一大批杰出的朱子学者。朱子学不仅在江户时代前期的日本思想界占据着中心地位,甚至也可以说,当时整个东亚世界朱子学研究的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了日本。
从江户前期到现在又已过去四百年。在这段时间里,朱子学在日本虽然最终并未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其命运甚至也可说几经盛衰沉浮,但对朱子学的研究在日本却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屡有创获。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充分吸收和消化其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今后深入推进朱子学研究所需面对的课题。而当下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在继承原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在发生着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
本文将目光投向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的成果,从中或可窥看当下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某些特色和动向。根据这一年成果的分布情况,本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有关文献考证、经学解释、家礼实践和文化交涉等议题上。
1.种村和史:《严粲诗辑所引朱熹诗说考》
众所周知,朱子《诗经》研究经历过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对小序(相传为子夏所作)的态度:“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朱子语类》卷八十)其最终成果即为今本《诗集传》,该书完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而在此之前的“诗解文字”则已亡佚。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朱氏集传稿”,另外朱子曾说:“《诗传》两本,烦为以新本校旧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朱文公续集》卷八《与叶彦忠书》)其中的“旧本”所指当与前述“诗解文字”和“朱氏集传稿”相同,束景南称之为《诗集解》。旧本中与新本不合者均被朱熹废弃。《诗集解》虽不传,但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1182年朱熹、尤袤序刊)(以下简称《吕记》)、段昌武《毛诗集解》以及严粲的《诗辑》等书保留了《诗集解》的逸文。束景南据上述三书,辑录了《诗集解》逸文。[1]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种村和史的《严粲诗辑所引朱熹诗说考》一文即是对严粲《诗辑》所引朱子诗说的研究。[2]严粲(生卒年不详)[3]撰写了《诗经》注释书《诗辑》(淳祐八年,1248年自序刊本),种村论文的核心是辨别严粲所引朱熹诗说中的新说和旧说。不过种村也指出,他是按照学界通行的做法,将《诗集传》以前,尊重小序阶段的朱熹诗说统统放在《诗集解》的名下加以讨论,因此《诗集解》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具有一定的“假想的性格”。
《吕记》所引朱子之说为旧说,当属无疑。[4]但严粲和段昌武所引则有讨论的必要。种村在第一节“问题设定”的部分介绍了先行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观点。束景南认为段昌武和严粲“二人均为主毛序说诗派,二书亦皆仿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而成……故二书中所引‘朱曰’、‘朱氏曰’,必为朱熹主毛序说之《诗集解》,而非黜毛序说之《诗集传》”[5]。彭维杰则认为:“如较朱子晚出多年之严粲,所著《诗辑》,引朱子说者五百余处,其间有引朱子旧说……亦有引朱子晚年定说者……欲探严氏引朱子旧说、新说,则必先考其引文别其新旧。”彭维杰证明所引为旧说时提供的依据是“吕氏《读诗记》引文同”,而新说的依据是与定本《诗集传》相同,但是“未见吕氏《读诗记》引之”。[6]种村指出,若按彭维杰之说,则束景南的《辑录》中混杂了朱子的新说,与此同时,彭维杰之说也存在问题:“吕祖谦在朱子的诗说中选择于自己有用的部分加以引用,其所引用的并非朱子旧说的全部。因此不能仅因不见于《吕记》便断定其为朱子的新说。”[7]严粲所引朱熹诗说,若要确定为新说的话,需要满足如下的条件:《吕记》在相应的地方不仅没有引用这一说法,反而引用了与此说完全不同的朱熹的另一说法。这一看法构成了种村全文论述的一大支柱。
在第二节“比较的方法和判别的基准”部分,种村在理论上将严粲所引朱子诗说的来源分为四类:1.转引自《吕记》;2.引自《诗集传》;3.引自《诗集解》本身;4.引用来源不明。他将严粲所引朱子诗说共计589例与《吕记》所引朱子诗说、朱子《诗集传》进行对比,指出实际存在的五种情况,并制成如下表格:
种村总结道:“在旧说与新说不同的前提下,2.1、2.2和4,严粲所据为旧说;3.2所据则为新说。这也表明,站在尊序立场上的严粲,将持反序姿态的《诗集传》作为参考资料而加以使用。”[8]而589例引文具体情况则附于文末附表《〈诗辑〉所引朱熹诗说一览》中。
种村在第三节“三书关系的实例”中举出实例,第四节从“《诗辑》所引朱熹诗说的多样性”“《诗辑》所引《诗集解》逸文的数量”“严粲对朱熹新说的接受”“严粲对朱熹诗说的重视”“朱熹诗学的影响力”和“《诗辑》所引朱熹说的校勘价值”六个方面概括了“考察所得以了解的事项”。如第五项,种村指出,朱熹对后世学者而言是具有多样性的巨大存在:“不仅是否定了诗序,在《诗集传》中以自己的思想重读《诗经》的朱熹,而且是他自身决意废弃的,基于诗序的《诗经》注释,也同样持续地强烈影响着后世的学者。”[9]
第五节,种村探讨了严粲得到《诗集解》的途径。种村质疑了束景南《诗集解》曾刊刻流传的观点,认为其只是以手稿形式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流传。至于该书如何传到严粲手上,因为史料不足,目前无法推断。第六节,种村简单介绍了遗留的课题和未来的研究计划。总体而言,全文材料充实,论述清晰,观点鲜明,可以说不仅对先行研究进行了修正和深化,而且尽可能地对《诗辑》所引朱子诗说的时期逐一进行了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材料。
2.鹤成久章:《关于<四书纂疏>所引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
南宋末期赵顺孙(1215—1277)所撰《四书纂疏》26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所引朱子之说均注明出自何书,如“语录曰”“文集曰”“易本义曰”等(明代永乐朝编纂的《四书大全》亦引用了《纂疏》但却隐去出典,径改为“朱子曰”);其引自《语录》者亦有不见于今本《朱子语类》或与其文字不同的;保留了不少朱子后学中已散佚文献的逸文。在关注到这些事实的基础上,鹤成久章《关于<四书纂疏>所引的朱子学文献——以<朱子语录>为中心》[10]一文,以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朱子语录》为核心进行了考察。
鹤成在第一节主要考察了《四书纂疏》的成书年代。从为其作序的洪天锡去世于咸淳三年(1267),可推断该书写成于1267年之前。而在全书出版之前,牟子才为《中庸纂疏》所作序文写成于宝祐四年(1256),且该序提到了《大学章句疏》(即《大学纂疏》),因此《大学纂疏》和《中庸纂疏》应于1256年前后完成。从内容可看出,洪天锡的序是为《论语纂疏》和《孟子纂疏》而写,且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二所收应俊的序,可知《大学纂疏》和《中庸纂疏》率先完成并出版,等《论语纂疏》和《孟子纂疏》完成之后又合并出版。[11]
鹤成在第二节考察了《四书纂疏》所收朱熹及其后学13人文献的情况。如陈淳的《大学口义》《中庸口义》和《语录》已经散佚,但《四书纂疏》保留了大量应是其逸文的资料。鹤成最后总结认为:“朱熹以外的学者的著作被引用之际虽并未明示书名,但《四书纂疏引用总目》所举之书很多已散佚,若将这些引文掇拾整理的话,应是研究朱熹后学‘四书’注释以至整个思想的有益资料。”[12]
第三节,鹤成考察了《四书纂疏》与元明各种‘四书’注释集成类著作之间的关系,指出《四书集注大全》所收朱子及其后学13家的引文很多可以追溯至《四书纂疏》。[13]他在一个注释中还举例道:“《四书集注大全》中源自《四书纂疏》的引文相当之多。略举一例,通常《四书集注大全》引黄榦之著作或语录时称‘勉斋黄氏曰’,引陈淳之著作或语录时称‘北溪陈氏曰’,如果仅称‘黄氏曰’或‘陈氏曰’,则其引文的来源当是《四书纂疏》。”[14]
第四节,鹤成考察了《四书纂疏》所引《朱子语录》的资料价值。今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大全》成书于咸淳六年(1270),《大学纂疏》《中庸纂疏》成书于1256年左右,其时赵顺孙当没有看到《语类大全》,显然使用的是其他《语录》或《语类》。《论语纂疏》和《孟子纂疏》成书于1267年前,赵顺孙也应该未看到《语类大全》。至于赵顺孙参考了何种《语录》,从其《大学纂疏》“读大学章句纲领”“大学章句序”(《中庸纂疏》同)以及《论语纂疏》《孟子纂疏》“读论孟集注纲领”“读论语孟子法”来看,很可能是沿袭了始于黄士毅的语录分类形式,如此则赵顺孙至少看到过《蜀类》或《徽类》。鹤成还分析了一些见于今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大全》和不见于今本,可能源自赵顺孙所看到的古本《朱子语录》的引文,他也指出这些引文不少是断片,有些可能仅是门人提问语而非朱子的答语。[15]
第五节,鹤成指出了数量在2000条以上的《四书纂疏》所引朱子的语录(当然很多是极短的断片式语句)的一些特征。如在黎靖德《语类大全》中以小字形式出现的引文,在《四书纂疏》中大量存在;《语类大全》记载两人所录的语录,在《四书纂疏》中有整合为一条语录的情况;《语类大全》所载一条语录,在《四书纂疏》中有分多处出现的情况;对于陈淳和徐寓所录,《语类大全》多采陈淳录,而《四书纂疏》则用徐㝢录;虽为“语录曰”,但却见于今本《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书(知旧门人问答)的情况也存在。[16]
除了上述分析以外,鹤成论文还详细列举了记载赵顺孙生平资料的文献、《四书纂疏》的各种版本、《四书纂疏》所引朱子后学13家著作的存佚情况以及日本学界研究《朱子语录》的各种文献,若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话,该文乃是有益的参考。另外顺便一提,作为其参考资料之一的佐野公治《<四书>学史的研究》也于2014年年底出版了中文本(张文朝、庄兵译,林庆彰校订,台湾万卷楼图书出版,2014年11月)。
3.福谷彬:《关于<资治通鉴纲目>与朱子的春秋学:以义例说与直书的笔法为中心》
关于《春秋》这一经典为何而作以及如何作成的问题,朱子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语类》卷八十三)朱子认为《春秋》是孔子依据未修之鲁史《春秋》而作,其手法为“直书”:“《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同上)既为“直书”,故朱子一方面认为古文经学记事之凡例、变例之说多不可信:“《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同上)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今文经学寓褒贬于一二字之间的议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同上)而被问及“《春秋》当如何看”这一问题时,朱子的回答也显得非常干脆:“只如看史样看。”(同上)
朱子并未如《诗集传》一样留下《春秋》的注释,但他及其弟子赵师渊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却与《春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其“纲目”的结构设置与《左传》的“经传”颇为一致;另一方面,在“纲”的部分朱子也用了《春秋》的笔法,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例和笔法做了修正。故《纲目》亦可称为朱子《春秋》学的代表性成果。
不过,朱子上述“义例说的否定”和“直书笔法的肯定”的立场,与其在《纲目》中采用的褒贬笔法以及数量庞大的《凡例》之间,却不免存在着隔阂。这正是福谷彬《关于<资治通鉴纲目>与朱子的春秋学:以义例说与直书的笔法为中心》[17]一文的问题意识所在。[18]而他的思路在于:设置“义例说与直书说的再检讨”和“《纲目》凡例与朱子的春秋学说”两节,在分别考察朱子《春秋》学解释的立场和《纲目》所运用笔法的基础上,将这两者调和,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一贯性。
不过,福谷所设定的核心问题是:朱子否定今文经学作为“褒贬”的解读方法的“义例”与其在《纲目》中所使用的“褒贬”笔法及其《凡例》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并未涉及上文提到的朱子对古文经学“传例”的怀疑。相反,福谷在第一节中,恰恰强调了朱子对于这些“传例”有所继承的另一面。福谷指出朱子曾述及西晋杜预之语“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并认为其所指的内容不外乎就是杜预《春秋序》说的“凡例”。“凡例”又称“正例”,是孔子作《春秋》之前已经存在的“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倘若孔子所修《春秋》经文并未按照这些“正例”书写,则称之为“变例”。而朱子对“变例”持否定态度。关于这一点,福谷引用了如下一段话:“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语类》卷八十三)福谷由此指出:“朱子否定存在‘变例’的同时,却也肯定了孔子在《春秋》中有表示褒贬的意思本身。
这也意味着,朱子虽然否定‘一字褒贬’的存在,但认为孔子有着借直书历史以表示褒贬的意图。”[19]
福谷对“义例说的否定”这一全文基本前提的含义进行了厘清:“朱子否定《春秋》的义例说,其所否定的是与‘正例’不同的‘变例’,但对于孔子笔削以前即已存在的‘凡例’的存在却持认可的态度。”[20]不过应指出的是,杜预所概括的凡例,是否均为孔子以前所存在,抑或有孔子所创设的部分,实已难以断定。朱子认为可疑的也不仅限于“变例”而已,且杜预所说的“变例”也并非公羊学的“一字褒贬”。故将朱子之说概括为“义例说的否定”显得过于宽泛,而收束到“变例说的反对”则似又过于狭隘和偏颇。
福谷还引用《文集》卷六十《答潘子善》中如下一段话,以揭示朱子对《春秋》成书过程认识的最终“定论”:“某谓《春秋》为圣人褒贬之书,其说旧矣,然圣人岂损其实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书之耳……或以为若是则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圣人而后作哉?曰:《春秋》即《鲁史》之旧名,非孔子之创为此经也。使史笔之传举不失其实,圣人亦何必以是为己任?惟官失其守,而策书记注多违旧章,故圣人即史法之旧例,以直书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实耳。初未尝有意于褒之贬之也。”[21]须指出的是,本段引文非朱子之语而为潘子善之语。潘子善此说不能成立实属显然。如其所说,则孔子之《春秋》仅为一不失其实之“史”而已,又何足为“经”?而孔子之功又岂在纠正历史记录之失实哉?其答语显然不足以回应或人“何待圣人而后作”的提问。《鲁史》旧名为《春秋》,孔子之所修仍名为《春秋》,但这又何妨圣人置褒贬于其间而别为一经?故其说又何能驳“《春秋》为圣人褒贬之书”?
在前文有关“变例”的引文中,朱子明确说“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朱子亦不得不承认圣人有意褒贬,准此则其“直书说”实不能成立。“‘……《春秋》只是旧史录在这里。’蔡云:‘如先生做《通鉴纲目》,是有意?是无意?须是有去取。如《春秋》,圣人岂无意?’曰:‘圣人虽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为之说不得。’”(《语类》卷一百二十五)朱子此说只能说明不当妄说,而并非证明圣人乃是无意之直书。故正如蔡季通之说,朱子因《资治通鉴》而作《纲目》和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均是有意褒贬,两者本相互贯通,没有矛盾。唯朱子所倡无意之“直书说”则未免与其“有意褒贬”的主张和做法有所矛盾而已。
4.新田元规:《程颐、朱熹祖先祭祀方案中身份的含意——以元明人的评价为线索》
朱子作《家礼》,以此为代表的宋代礼制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杨志刚在其《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将此变革称为“礼下庶人”[22],吾妻重二在《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以<家礼>为中心》一文中将这一变化称为“仪礼的开放”,认为其与朱子学“圣人可学而至”这样的观念有关,并着重强调了家礼对于士庶各阶层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23]新田元规的《程颐、朱熹祖先祭祀方案中身份的含意——以元明人的评价为线索》一文[24]则强调了与之不同的另一面,即对于士大夫而言显示身份的特殊含意。
新田认为:“‘以万民具有成就道德的可能性为前提’的普遍的性格,与‘重视以地位、道德和教养为基准的身份’的差异的性格,原本在儒教的理论中就带有矛盾意味地共存着,在宋人的道德论和礼说中,这两方面的纠葛也并未消解而依然存在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本文极力要注目于在宋人的祭祀构想中,其设想的实践主体是连庶人也包含在内的所有身份的人,还是最多仅限于士大夫这一微妙的差异。”[25]这一视角受到著名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揭示的“以身份显示为目的的仪礼实践”这一问题的启发。伊佩霞指出,家礼实践不仅为了陶冶道德,也是为了防止重新掉入无教养阶层,士大夫期望家礼具备显示社会地位差异的功能。而这一身份区别的含意未必一定被宋人清晰地意识到或者说出来。伊佩霞认为中国整个传统社会中礼制担负身份区分的功能,新田认为以此为基础,至少可以推测在宋人的礼说中,包含着“覆盖庶人的教育”和“士大夫身份的表示”这样的多义性。而身份的含意即祠堂祭祀是士大夫阶层特权性的象征这一点,被元明时代朱子的后继者们明确论述出来。新田本文的目的正是要以元明时期的礼说为线索,将内在于宋人祖先祭祀说中身份的含意予以揭示出来。[26]而本文所选取的原始文献则是元末至明代《祠堂记》一类的文献。
全文分三节,第一节,新田确认了元明人认为宋人祖先祭祀方案的划时代性在于其士庶通用的一律性,探究了他们是如何论证轻视身份差别的祭祀方式的正当性的。第二节,指出关于身份的一律性的优点究竟为何存在着普遍性(万民的教化)和特殊性(适应于流动性社会中的士大夫)这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三节,具体分析上述主张特殊性的观点,指出与其教养论中存在的两面性相对应,宋人祖先祭祀方案中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普遍性和实质上的特殊性这两面。而与道德教养论领域里明学的展开并行的是在祖先祭祀领域里,通过简略化与习俗更进一步妥协,从而将“教民报本”这一普遍性加以实质化的推进。[27]
在行文中,新田引述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如第二节所讨论的是舍弃身份条件的意义究竟是在“包含所有身份”还是“应对流动化”。新田的引用中就包含了明代著名学者丘濬在《家礼仪节序》和另一篇祠堂记中的侧重点并不相同的说法。丘濬在《家礼仪节序》中强调:“汉魏以来,王朝郡国之礼,虽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则荡然无余矣……文公先生因温公《书仪》,参以程张二家之说,而为《家礼》一书,实万世人家通行之典也……夫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世之学儒者,徒知读书而不知执礼。而吾礼之柄遂为异教所窃弄而不自觉。自吾失吾礼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间,阴窃吾丧祭之土苴,以为追荐祷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经术者,亦且甘心随其步趋,遵其约束,而不以为非。无怪乎举世之人,靡然从之,安以为常也。”新田指出丘濬在此强调的是:“在仪礼领域里应当抑制异端的侵蚀,朱熹制定了包含所有身份的人的礼制,力图重建礼的秩序。”即通过适当简化礼仪,使大众均能得到“教民报本反始”这样的教导。而丘濬自身的《家礼仪节》就是在简化的方向上将仪礼加以改订,而谋求“万世人家通行之典”的实质化。[28]
不过新田随即指出:“可是,同样是丘濬,对于朱熹《家礼》的特征‘身份的一律性’,却显示了与《家礼仪节序》重点不同的另一认识。丘濬在祠堂记中,不提‘教民以正确的祖先祭祀方法’‘在仪礼上排除异端的影响’这样的论点,如下文所看到的那样,设定了‘构想能够应对身份的不安定化的祭祀方式’的课题,论述了祠堂祭祀说的意义。”[29]新田接着引述了丘濬的如下一段话:“古人庙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数,上下咸有定制。粤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无土,是故父为士而子或为大夫,父为大夫而子或为士,庙数不可为定制。且又仕止不常,迁徙无定,而庙祀不能有常所。汉魏以来,知经好礼之士,如晋荀氏、贺氏,唐杜氏、孟氏,宋韩氏、宋氏,或言于公朝,或创于私家。然议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变;或为之于独,而不能同之于众;或仅卒其身,而不能贻于后。此无他,泥于古,便于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马氏,始以意创为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创之主,定为祠堂之制,着于《家礼》通礼之首,盖通上下以为制也。”[30]实际上新田全篇论述的一大核心论据,正是来自丘濬的这一段引文。把握了这一点,新田全篇的论旨也就一目了然,无须赘言。
5.吾妻重二:《東儒教文化交涉:觉書》和《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
吾妻重二《东亚的儒教与文化交涉(笔记)》一文[31]从“文化交涉学”的视点出发,勾勒了东亚儒学和东亚朱子学的多个侧面,反映了近年学界悄然兴起的“文化交涉学”研究的新动向。至于作者所说的“东亚”,则指的是中国、韩国、朝鲜、越南和日本这一在古代就有广泛交流的,可称之为“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的地区。并且作者论述的并非儒教整体,而主要是近世的儒教,其中的核心无疑就是朱子学的兴起和展开。“近世”指的是近代以前具有一定的社会体制且维持较长时间的时代。就中国而言,近世自10世纪宋代以降,韩国则是朝鲜王朝后期(17世纪以降),越南是黎朝(15世纪)以降,琉球则是萨摩入侵以后(17世纪),以及日本的江户时代(17世纪以降)。
吾妻在第一节“儒教史的研究与儒教通史”中回顾了以往将儒教置于亚洲或者东亚视域中进行研究的一些尝试或者提议。他提到了1990年6月岩波书店《思想》杂志《儒教与亚洲社会》特集,以沟口雄三为核心的当时第一线的研究者对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儒教各个方面的研究。吾妻称自己当时并没有充分应对“亚洲”这样大范围的准备,同时也因为这些论文多是个别研究而没有加以一般化,即使读了也只是处于消化不良的状况。不过24年这样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以后再回头来看,发现所收的论说相当有趣。不仅论文如此,今井昭夫等人编的《儒教关系史年表》和渡边浩《东亚儒学关联事项对照表——19世纪前半期》等也以其对于事实的简洁介绍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具有给人启发的作用。[32]而在户川芳郎、蜂屋邦夫和沟口雄三执笔完成并由山川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儒教史》中,虽然所讲述的仅仅是中国的儒教,但是却未冠以“中国儒教史”之名,将中国与儒教直接等同,而未考虑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也有儒教。吾妻也由此推测其时沟口或尚未有关于东亚儒教史的构想。
吾妻还回顾了较早提出有必要进行东亚儒教研究的岛田虔次。他在1967年出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后记中说道:“像基督教史多是在泛欧洲视野下写成的一样,儒教史、朱子学史也应首先作为贯通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通史来写……写出将这些方面都合法正当地纳入视野范围内的儒教史、朱子学史,才是当前的急务。”[33]不过遗憾的是,岛田生前并未完成这一设想。吾妻还提到了切入东亚儒学研究的一位前辈学者三浦国雄,其在《朱熹》(人类知识的遗产系列丛书,讲谈社,1979年)一书的终章以“对后世的影响——朝鲜朱子学的展开”为题,对朝鲜朱子学进行了素描。现在看来其论述虽并不充分,但其可贵的尝试在那个时间点的其他著作中却是看不到的。
吾妻指出:“讽刺的是,以前由于研究滞后,撰写通史的材料不足;而今由于个别研究大大推进,资料过度膨胀得写不了通史。”不过,作者认为:“撰写那样的通史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而且也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一方面,由各国儒教研究者分担执笔拼凑而成的并不足以称之为通史;另一方面,应该在怎样的构想下进行撰写,笔者也尚处于犹豫的阶段。从‘以儒教为中心的知的世界’这样说起来则无限广阔的前提出发,对于当前已被研究的人物、著作和思想的特色这样基本的事实的叙述,以及相关的书志学的把握本身,应当都是必要的。”[34]
在第二节“关于‘文化交涉’”中,吾妻首先介绍了与东亚儒教研究有关的研究动向,尤其是作为其起点的三个大型研究计划。第一,2005—2009年由小岛毅领衔的文部省特定领域研究“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跨学科的创作”(简称“宁波”)、2005年创设,由黄俊杰领衔的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以及2007—2011由陶德民领衔的关西大学文部省G-COE“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吾妻自身即是第三个计划的成员。其相关机构设施有国际性学会“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的事务局、关西大学新创设研究生院东亚文化研究科及其纪要《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和研究生论集《文化交涉》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论文集,其中不少涉及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和展开。[35]这三大计划已经和正在推出的成果以及这一领域的其他成果一起,为继续开展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吾妻接着阐述了“文化交涉”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有关“文化”的定义往往只是突出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的,或者只是在静态中把握文化。吾妻则指出,文化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不断流动的。并且基于“文化是通过交涉而形成,而并非原本就固定在那里的”这一基本事实,主张在考察文化时,从“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视点,尤其是与其他地域的接触和交涉的视点来看。这样的研究其实就是要探明,异文化是如何通过接触而被理解、接受,产生影响或最终被加以改造的。[36]
在第三节,吾妻就自身近期关注的几项具体议题——“朱子学的传播与变容”“朱子学的普遍性”“关于周敦颐”“书院、私塾”和“《家礼》的冠昏丧祭仪礼”介绍了“近世东亚儒教的诸相”。作者将其中部分内容融入进《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中,并作为2014年3月15日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朱子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公开发表。[37]其有关朱子学在韩国、越南和日本传播的介绍简洁扼要,无论是想要进入这一领域做深入的研究,还是仅限于浅尝辄止式地了解,都极具参考价值。
在结语部分,吾妻强调:“在谈及东亚的儒教之际,文化交涉的方法以及视点是非常有用的。”接着文章归结到这样一点上:“这样来看的时候,也让人注意到将儒教视作文化来看待这一点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思想的儒教’,不如说是‘作为文化的儒教’当然不能忘了作为思想的儒教,考察儒教具有的理论和哲学是必要的,不过这样的看法过于强烈的话,有关的文化事象就有可能会被忽视。……过去在这一区域里,共享了超越地域和时代的儒教文化,我们也有必要在广阔的视野中揭示其样态。”[38]当然,这样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朱子学。正如吾妻所说:“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39]
吾妻曾长期专注于中国朱子学、宋代思想和仪礼的研究,现在身体力行“文化交涉学”的理念,不仅将视野拓展到日本,而且也几乎是从头开始学习韩国和越南的儒教,全身心投入名副其实的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儒教”研究之中,其求知欲、魄力和毅力之强均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6.其他成果概述
以下快速扫描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的其他成果。
儿玉宪明《朱熹律吕新书序注解》[40]是对朱熹《律吕新书序》所做的校勘、日译和注释。关于蔡元定所著《律吕新书》作者已刊行有关的注解、序文和《律吕新书》原文都采用《性理大全书》所收本。该文是属于文献的基础研究。而有关朱子学乐律方面的研究应该说也尚不充分,有待学界今后推出更多相关成果。
现代汉语中,作为不定冠词标识的数量词被置于名词之前,为了揭示这一标识形成的过程,木津祐子在《作为不定冠词的“一个”的成立前史——<朱子语类>的场合》一文中以《朱子语类》为对象进行了分析。她发现:“‘数量词+名词’这一形式尚未具有不定冠词的功能,而且,名词‘人’和量词‘个’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前面的数词仅限于‘一’;这与将‘一个’置于抽象名词之前是类似的;而且当‘一个’被置于除了‘人’字以外其他表示‘人’的意思的词之前时,这个词之前通常还带有修饰语,即‘一个’与修饰语具有容易共起的关系。在《朱子语类》中,‘个’并非是用于计算‘人’之数的量词,其主要的功能是在文脉中突出名词所具有的属性。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这种文脉所要求的属性与‘一个’共起的现象,与数量词作为不定冠词的标识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41]
中嵨谅《陈亮与陆九渊——朱熹论敌的思想》一书[42]目录如下,序章《先行研究与笔者的立场》;第一部《陆九渊》:第一章《陆九渊思想中的自立与他者的修养》,第二章《陆九渊思想中的讲学与读书》,第三章《陆九渊的春秋学——以与其高第杨简的对比为线索》;第二部《关于<象山先生文集>的诸本》;第三部《陈亮》:第一章《陈亮的政治批判——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书>再读》,第二章《陈亮对历代为政者的评价》,第三章《从陈傅良来看朱陈论争》;终章《陆九渊与陈亮:其出发点的共同性》。[43]
在朱子学文献的翻译方面,2014年亦有可观之处。除了大规模推进的《朱子语类》(以及《文集》)翻译以外,另有两部朱子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土田健次郎翻译的《论语集注》共四册,从2013年出版第一册开始,2014年先后出版两册,至2015年春出版第四册,至此全部出齐。[44]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在翻译和注释朱子《论语集注》之外,还以“补说”的形式引用了日本江户时代与朱子学立场相左的“古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论语古义》和荻生徂徕(1666—1728)《论语征》的观点。这样做的确有助于读者理解朱子注释的独特之处。[45]另外细谷惠志翻译的《朱子家礼》也于2014年出版。[46]
总结和展望
与前几年似乎“沉寂”的现象不同,可以说今年日本学界在延续原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极探索新的突破口。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这一年日本学者朱子学研究的某些特点。
第一,注重文献的基础研究。对中国学界来说,日本学者向来以擅长考证功夫著称,这一点在2014年的研究中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文献的基础研究将为思想研究提供适当的材料,思想研究也唯有在恰当地把握和运用材料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今年的众多著述中,种村和史、鹤成久章、儿玉宪明的三篇大致可归入文献考证类作品自不必说,其他研究也贯穿着对于文献材料的搜集和考察,如新田元规发掘和运用元明时期“祠堂记”这类看似只对历史研究有价值而向来极少受思想研究者注意的文献,而在思想研究上收获宝贵的结论,就堪称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另外,从词汇学、语法学的角度研究《朱子语类》的方法,近来在中国学界似乎相当盛行,日本学界如老一辈的元曲研究专家田中谦二也曾将《朱子语类》作为“语料”进行研究,并进而转入朱门弟子师事年代的考察,而大有创获。对于以思想分析为主的传统思路而言,这一语言学研究的进路或许也能发挥让人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第二,重视朱子的经学思想。2014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的重心无疑是朱子经学的研究。例如,种村和史涉及了朱子《诗经》注释的发展变化,福谷彬论及朱子的春秋学,鹤成久章有关《四书纂疏》引文的考察,都触及了朱子的经学文献。另外,有关礼乐的文章也包含了朱子的经学思想。有关朱子经学的研究,将是朱子学研究有待深入推进的重要课题,日本学界的这些成果也将给我们提供有益参考。
第三,关注礼乐实践的层面。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传统以“理气心性”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研究取向,2014年日本学界对于“形而下”的具体实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正如吾妻重二指出的那样,朱子学具有一个文化体系所包含的广度。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哲学思想的朱子学,但是近来对于朱子学在实际生活层面的影响越发关注。2014年不仅有多篇论文关注了礼乐实践层面的问题,而且《朱子家礼》也被翻译成现代日语。新田元规关注了程朱理学祭祀礼仪中的身份等级问题,儿玉宪明更是将视角转向中国主流哲学界很少关注的《律吕新书》和朱子学的乐律、音乐思想。吾妻重二则在东亚儒学的领域中谈论了朱子家礼的传播。实际上,在异域如何具体实行中国传来的礼乐,是困扰这些学者的重大问题,而且能否付诸操作的问题还会影响他们对朱子学的理解和信任。从理论上来说,礼乐能否实践的问题,也牵涉到朱子学或者儒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如何与各地域的特殊性结合的问题。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更对东亚世界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构建文化交涉的视野。朱子学不仅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而且对东亚世界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拓宽朱子学研究的视野,不仅应当像鹤成久章、新田元规一样,将朱子学置于宋元明清这一纵向连续的历史演变中加以考察,而且也应当如土田健次郎一样,在研究朱子学之际,能够横向扩展,关注诸如仁斋学、徂徕学等中国以外地区的朱子学注释和研究。正如吾妻重二所提倡的“文化交涉学”的视野和思路,我们应该积极关注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地的朱子学,充分把握朱子学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文化交涉学的视野和方法正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这种丰富内涵和多元特色。而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实际上也正是朱子学所蕴含的普遍性的具体体现。从江户初期藤原惺窝等人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朱子学具有普遍性这一特点。他们不仅对朱子学倡导的普遍性观念进行思考和体认,并且也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吾妻介绍的三大计划以外,自2013年起,中国大陆也首次以“国家项目”的形式推动日韩朱子学的研究,这也预示着东亚朱子学或东亚儒学的研究将在未来获得更深入的推进,同时也为中国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推进甚至再次成为朱子学的中心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构筑起新的研究平台。种村和史和鹤成久章的文献研究不仅展示了日本学者扎实严密的文献考证功夫,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于基础性文献研究的耐心和毅力,也颇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研究,还为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做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平台,指示了方向。如借助于种村的研究,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1.将其方法运用于对段昌武《毛诗集解》的研究;2.从严粲对旧说、新说的取舍看严粲《诗经》学研究的特色;3.就朱子旧说、新说的差异,探讨朱熹《诗经》学形成发展的过程;4.朱子《诗经》著述的版本、流通与影响。而对于鹤成所梳理的朱子及其后学的文献,我们不仅可以从文献的角度继续对其加以深入系统的分类和整理,而且也可将其运用于对朱子及其后学的思想研究中。而且《四书纂疏》本身对早期《朱子语录》形成史和朱子后学思想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显然也还有待我们加以充分发挥。而吾妻重二所揭示的“文化交涉”的视野和方法,实际上也对朱子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总之,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新的研究的“生长点”,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做法。
第六,充分利用中国学界的成果。放在整个战后70年日本中国学研究史的视域中来看的话,近年来的这一特点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47]较早的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等自不必说,前几年朱杰人领衔出版的《朱子全书》(2010年修订版)等也都成为日本学者使用的必备参考资料。[48]当然对中国学者的成果,日本学者虽也有所辨析甚至批评,但其问题关注点却往往也与中国学者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有一致之处。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学者在研究和出版领域的成果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或认可,在朱子学研究的领域里中日学界的互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趋势也相当明显;但另一方面也督促我们更加积极地吸收日本学界的已有成果和关注其最新动态,在互动中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业绩。《朱子学年鉴》设置“当年各国各地区朱子学研究综述”这一栏目,其目的也无非是加快互动的频率,促进研究成果的传播。
本文在涉及作者问题意识或文献考证等处“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其意图也无非是希望不仅能概括介绍其成果及思路,更能引起读者阅读原文或者就相关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兴趣。至于这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虽也多有评论,但其是非得失,最终也仍有待读者的评判。
(附记:本文写作于撰写博士论文的紧张阶段,写作中恐未必能充分领会作者的原意以及深入准确分析所涉的各个问题,亦请读者与作者见谅,而文责在我则属无疑。另外,王玉、廖明飞、陈佑真、胡珍子等同学帮助复印了许多资料,在此也对其深表谢意!)
附注
注释:
[1]关于3月14—15日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举办之“朱子哲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纪要,可参史甄陶:《“朱子哲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2014年第9卷第2期,第33—36页。
[2]此文系由演讲稿整理出版,见吾妻重二著,傅锡洪译:《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2014年第9卷第3期,第15—22页,引文见第15页。
[3]同上文,第19—22页。
[4]此文系由演讲稿整理出版,见朱杰人:《<朱子家训>的普世意义》,《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2014年第9卷第3期,第27页。
[5]李蕙如:《许衡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96—97页。
[6]同上书,第119—121页。
[7]同上书,第125—130页。
[8]同上书,第133页。
[9]同上书,第135页。
[10]同上书,第137—139页。
[11]同上书,第144页。
[12]同上书,第198页。
[13]金永植:《科学与东亚儒家传统》,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
[14]许朝阳:《挂搭与相衮:朱子的理气型态及其对“恶”的处理》,《东华汉学》2014年第19期,第157—194页。
[15]王雪卿:《朱子工夫论中的静坐》,《鹅湖》2014年第39卷第10期,第1—13页。
[16]冯兵:《情感性·宗教性·实践性——朱子礼学观的三重维度》,《哲学与文化》2014年第41卷第12期,第139—152页。
[17]姜龙翔:《论朱子诠释<国风>怨刺诗之教化意涵》,《台中教育大学学报:人文艺术类》2014年第28卷第1期,第1—22页。
[18]劳悦强:《<论语><先进>篇“屡空”辨》,《汉学研究》2014年第32卷第2期,第265—291页。
[19]陈逢源:《从五贤信仰到道统系谱——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圣门传道脉络之历史考察》,《东华汉学》2014年第19期,第121—155页。
[20]胡元玲:《朱熹对宋王朝南渡变局的省思》,《书目季刊》2014年第48卷第2期,第9—77页。
[21]黄俊杰:《儒家历史叙述的特质:朱子历史叙述中的圣王典范》,收入氏著:《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159—181页。
[22]黄俊杰:《儒家历史解释的理论基础: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收入氏著:《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第183—220页。
[23]蔡家和:《朱子与阳明的孟学诠释差异之比较》,《哲学与文化》2014年第41卷第5期,第19—45页。
[24]黄信二:《从朱子与阳明论蒯隤与卫辄比较朱王之“礼”论》,《哲学与文化》2014年第41卷第5期,第47—76页。
[25]张文朝:《渡边蒙庵(诗传恶石)对朱熹<诗集传>之批判——兼论其对古文辞学派<诗经>之继承》,《汉学研究》2014年第32卷第1期,第173—208页。
[26]傅锡洪:《“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探微——有关儒家天人合一之学之建构与解构的一项考察》,《宗教哲学》2014年第68期,第171—188页。
[27]姜真硕:《栗谷哲学与人物性同异论之成立》,《哲学与文化》2014年第41卷第8期,第23—40页。
[28]李演都:《湛轩洪大容的“人物均”论探究——朝鲜后期人物性同异论争的演变与其意义》,《哲学与文化》2014年第41卷第8期,第99—113页。
[29]姜智恩:《东亚学术史观的殖民扭曲与重塑——以韩国“朝鲜儒学创见模式”的经学论述为核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4年第44期,第173—211页。
[30]参见黄俊杰:《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收入氏著:《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第295—311页。(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注释:
[1]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为本文提供了许多书目资料及悉心指导。在此对其大力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田教授为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有关中国历史及思想研究方面的资深教授。
[2]Joseph A.Adler,Reconstructingthe ConfucianDao:ZhuXi s Appropriation ofZhouDunyi(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哦rk Press,2014).
[3]Daniel K.Gardner,Confucianism: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4).即其第五章《公元一千年后儒家传统的再定位:新儒学的教导》(The Reorientation ofthe Confucian TraditionAfter 1000 CE:the Teach-ings ofNeo-Confucianism) .
[4]Hoyt C.Tillman and Margaret Mih Tillman,“Remodeling ConfucianWedding Ritualsto Address China's YouthCulture Today: A Case oofUsingthe ClassicstoRespondtoRecalcitrantProblems”,TaiwanJournal ofEast Asian Studies 1 0.2 (20 1 3):221-246.
[5]殷慧、田浩(Hoyt Tillman):《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2期,第103—108页。
[6]田浩著,张晓宇译:《郝经对〈五经〉、〈中庸〉和道统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4年第24卷第1期,第73—94页。
[7]田浩:《〈朱子家训〉之历史研究》,收入朱熹著、朱杰人编注:《朱子家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47页。
[8]AnnA.Pang-White,“ZhuXionFamilyandWomen:ChallengesandPotentials”,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40.3(2013):436-455.
[9]JohnBerthrong,“XunziandZhuxi”,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40.3(2013):400-416.
[10]Shao-yunYang,“ReinventingtheBarbarian:RhetoricalandPhilosophicalUsesoftheYi-DiinMid-ImperialChina,600-1300”,Ph.D.dis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14.
[11]BackYoungsun,“HandlingFate:TheRuDiscourseonMing”,Ph.D.diss.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2013.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图书馆)
注释:
[1]束景南辑录的《诗集解》,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6册。
[2]见庆应义塾大学(即庆应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7号,2014年,第1—51页。该文是其获得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项目“南宋江湖派的综合研究”的成果之一。种村和史,毕业于庆应大学,现任教于庆应大学,是研究清朝考证学和《诗经》解释学史的学者。
[3]严粲是《沧浪诗话》作者严羽的族人,为南宋江湖派的一位诗人,与该派代表人物戴复古(1167—?)有交往。
[4]该书完成于吕祖谦去世的淳熙八年(1181)前,且朱熹在淳熙九年(1182)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中曾说:“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文集》卷七十六)
[5]种村论文,第3页,原文见束景南《辑录说明》,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9页。
[6]种村论文,第4页。原文见彭维杰《朱子诗传旧说探析》注4,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学志》1999年第3期,第77页。
[7]种村论文,第5页。
[8]同上文,第12页。
[9]同上文,第31页。
[10]见《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63—64期合刊,第291—306页,2014年。本文是其所获科学研究费补助金项目“永乐三《大全》的基础研究”和“明代乡试、会试《三场题目》的思想史考察”的成果之一。其所用《四书纂疏》是影印通志堂经解本《四书纂疏》(附引得),台湾学海出版社,1993年。本文所说《朱子语录》非指今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大全》,也不是某一特定的早期《语录》或《语类》,而是泛指《四书纂疏》“语录曰”引文的文献来源。鹤成久章,毕业于广岛大学,现任教于福冈教育大学,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世阳明学、科举和书院等。
[11]鹤成论文,第292页。
[12]同上文,第294页。
[13]同上文,第296页。
[14]同上文,注33,第304页。
[15]同上文,第296—298页。
[16]同上文,第298—302页。
[17]见《东方学》第127期,第66—82页。福谷彬,现为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朱子学等。本节完成后方知2013年的综述即已对此文加以评述,两篇评述尽可各行其是而并行不悖。
[18]见福谷论文引言和结语等,第66页和78页等处。
[19]福谷论文,注12,第80—81页。
[20]同上文,第70页。
[21]同上文,第70—71页,原文见注10,第80页。出处为《文集》卷六十,《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18页,该卷注39,《朱子全书》编者指出,浙本有“伏乞指教”等30余字,同上书,第2930页。此书本是就具体事件的解读请教朱子,故朱子的回答(见2919页)亦仅限于其所提问的具体事件,至于对其有关《春秋》成书的议论持何种意见,则付之阙如。
[22]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下揭新田论文第95页所引。
[23]收入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东の仪礼宗教》,东京:雄松堂,2008年,第99页。中译见吴震编译:《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第一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新田论文注6所引,第115页。
[24]见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编:《中国哲学研究》第27号,2014年,第94—124页。“含意”即英文implication。新田元规,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现任教于德岛大学,研究明清儒教。
[25]新田论文,第95页。
[26]同上文,第96页。
[27]以上为新田在“结论”中的部分论述,第113—114页。
[28]新田论文,第103页,丘濬引文原文见注25,第120页,出自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九《家礼仪节序》。
[29]同上文,第103页。
[30]同上文,第104页,丘濬引文原文见注26,第120—121页。原文出自丘濬《重编琼台稿》卷十七《南海亭岗黄氏祠堂记》。
[31]见《现代思想》第42卷第4号,2014年3月,第98—113页。该期是有关“现在何故讨论儒教”和“作为规程的儒教”等的特集,所收文章颇值得阅读。本文仅就吾妻此文略为介绍近几年来在东亚地区兴起的有关“文化交涉”和“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的研究动向。
[32]分别见《思想》第792号《儒教与亚洲社会》特集附表第2、10页。该期所收与朱子学有关的论文如沟口雄三《中国儒教的十个特征》、渡边浩《儒学史异同的一个解释——“朱子学”以降的中国与日本》和子安宣邦《朱子“鬼神论”言说的构成——儒家言说的比较研究序论》等对中国学者而言仍然很有参考价值。吾妻重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现任教于关西大学,主要研究东亚的儒教。
[33]该书中译可参蒋国保译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译文略异。
[34]《东亚的儒教与文化交涉(笔记)》,第100页。有关儒教通史不但必要而且可能的主张,令人不免联想起“东亚儒学”何以必要和可能的问题,可参考吴震《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1期,2011年6月;《东亚儒学刍议——以普遍性、特殊性为主》,《中国学术》第31辑,2012年。
[35]略举几例如下:《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2《东亚的书院研究》,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8年;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东亚的仪礼与宗教》(前文注23引书同),东京:雄松堂,2008年;吾妻重二、朴元在编:《朱子家礼与东亚的文化交涉》,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以及吾妻编著的收入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丛书出版的《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系列,从2011年至2015年初已经出版四册。
[36]按照一般的印象,很多人会认为这一立场方法主要对于中国周边的国家适用,因为人们不自觉地就会认为中国文化向来受外界影响比较小,是独立自发地形成的。但实际上佛教和西域文化以及后来的欧洲文化、日本文化对中国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甚至于即便是早期的中国主流文化——华夏文化,也是各个族群的文化交融碰撞而成,春秋战国时代,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和秦文化等的碰撞交融,最终才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并且透过《礼记》等文献可以看出,各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或多或少一直保存在儒家传统中。这些领域其实都有待于借助“文化交涉”的视点加以深入探讨。
[37]吾妻重二:《朱子学——巨大的知识体系》(傅锡洪译,吾妻重二修改),台湾大学《朱子学的当代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3月,及《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第32期,2014年9月,第15—22页;后以《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在东亚的普遍意义》为题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1—16页。为便于读者查找,本文引文参照《厦门大学学报》。
[38]《东亚的儒教与文化交涉》,第110—111页。
[39]《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在东亚的普遍意义》,第11页。
[40]见新潟大学东亚学会《东亚:历史与文化》第23号,第64—74页,2014年3月。儿玉宪明,硕士毕业于大阪大学,现任教于新澙大学,研究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佛教学。
[41]见《中国语学》第261号,2014年,第46—63页,引文即该文摘要,见第46页。木津祐子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现任教于京都大学,研究中国语言学。
[42]该书由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4年10月出版。中嵨谅,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现任教于学习院大学等,主要研究宋代哲学思想。
[43]由于时间关系,笔者未能通读此书,不宜妄加评论,以后有机会当补上。
[44]该书收入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第841、850、854、858卷,2013年10月至2015年2月出版。土田健次郎毕业并任教于早稻田大学,主要研究宋明和江户的儒教。至此可发现本年度作者出身大多数都是早稻田大学,虽专业院系不尽相同,也有不少人本科毕业以后便前往东大、京大等校深造,不过如此集中于早大,令人称奇。
[45]若欲将朱子与仁斋、徂徕论语注释对读,除了直接将他们的著作对读以外,还可参考源赖宽辑《论语征集览》(20卷附诸序1卷),前川六左卫门刊,文化九年(1812)。除上述三书外,《集览》还收了何晏的《论语集解》,可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网页上下载原文图像。
[46]由明德出版社出版。细谷惠志任教于立正大学,不过并非朱子家礼领域的专业研究者。
[47]与此同时,作者一般都会同时给出中文引文的原文及其日译,如果二者选其一的话,出现中文原文的概率似乎也要高于日译。这也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趋势。
[48]不过朱杰人主编的另外两套印量极少的《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和《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是否因为流传不广所致,鲜见引用。今后应引起学者更多的重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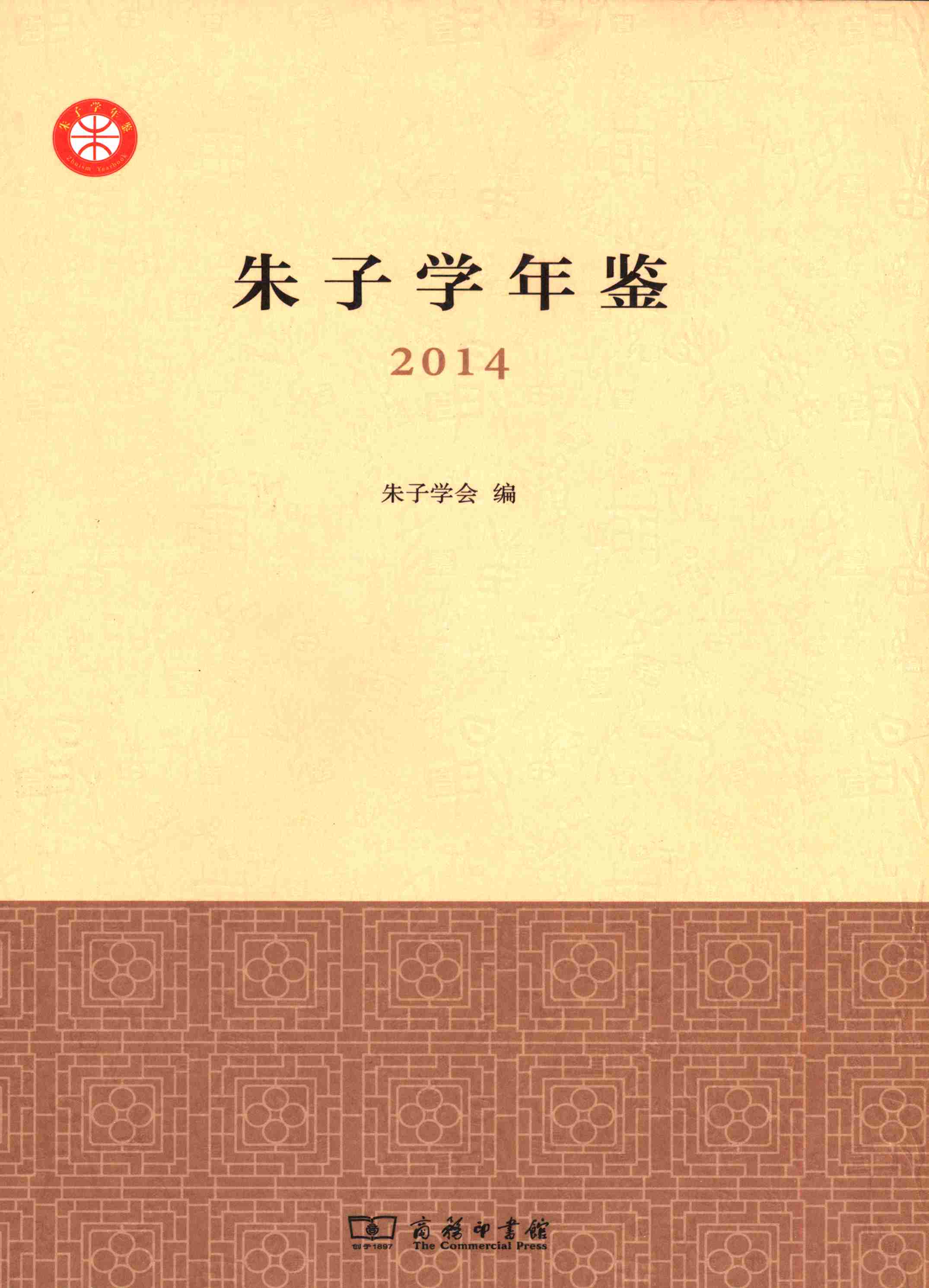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4》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分为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等九个栏目,收录了《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