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4》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680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048-05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宋代理学的形成是宋代最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但近现代却成为最被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这种差异在学术层面上的思考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使得理学的研究被划为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从而形成了理学形而上思维在哲学领域的探讨;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被断代史的分割所阻隔,导致对于宋代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思想史特征,而忽视了明清时期的研究。 |
| 关键词: | 宋代理学 朱子学 |
内容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被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笃信理学的人们,还是研究理学的人们,都可以从宋代理学的庞大体系中找出许多值得世人敬佩和践行的文化精神因素,甚至奉为治国之本;而近现代许多思想敏锐、富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学人们,却往往痛责理学家的“以理杀人”“以礼吃人”。其差异之大,实在令人诧异。
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容易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为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理学的形而上思维成了哲学家们思考和探究的核心内容,从理学家们的“文本”到研究者们的哲学结论,似乎成了现当代对于理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而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宋代的“思想史”特征,而研究明清史的历史学家们,注重于生长、生活于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各自欣赏、分别陶醉。
21世纪初,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撰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根据夫子自道,他撰写这部著作,就是有鉴于理学的哲学化使它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了家,更和儒学大传统脱了钩。因此,撰写此书,就是“企图从整体的观点将理学放回到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1]《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出版,也正如作者本人所预示的那样,为学术研究“提供另一参照系,使理学的研究逐渐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2]
然而遗憾的是,余英时先生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思考宋代朱熹理学的整体动态的演变过程,还是未能突破断代史的阻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们,固然全力重新建构“政治文化”与自身“内圣”修养的尊严而可贵的“道统”,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种尊严而可贵的“道统”,确确实实给后世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正是这些负面的影响,让现当代许多思想敏锐的学者们,产生了对“理学”弃之而后快的激愤心态。那么,从宋代到近现代,这中间即明清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好奇和思考。而这种思考,无疑应该首先打破断代史的人为阻隔,从长时段的演变历史来解读这一“理学”过程,或许是相当有益的事情。
一、宋代以来朱子学、理学的政治制度化变迁
宋代的理学家们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设计了深具儒家传统的道德标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试图把这些道德标准实践于现实政治、社会与个人。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宋代理学家们所设计的这些道德标准,基本上没有在宋代形成制度化的实践。这种制度化的实践,经历了元、明时期的不断演化。
元朝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华,亟须借助汉人的道统来稳定统治、治理天下,因此从忽必烈即位之后,就“大召名儒,辟广庠序”,修造孔庙,翻译和学习儒家经籍。其中兴学校之举,影响至巨。在许衡、耶律有尚等人的推动下,宋代朱熹等人所倡导的教育体制,在元代得到了实行。“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3]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学校,所教皆朱子之书。[4]元朝以朱子理学为知识范本的教育体制的推行,对于明清时期朱子学、理学演化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起到了过渡桥梁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实施,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有制度上的推行与保障。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后,以恢复汉官威仪为己任,宋代的道德标准自然成了恢复汉官威仪的最直接和最可行的政治、社会范本。于是,科举制度的重建,就自然而然地沿袭元代的理念,虽然说“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他起兵反元的鲜明口号,但是要想稳定统治,特别是官僚队伍的培养,就不能不追随于元朝之后,把宋代理学家们特别是朱熹的著作,确定为学子们进身仕途的必读、必考法定教科书。[5]换言之,朱熹等宋儒们的道德主张,很快占据着明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
为了强化这一意识形态,朱元璋还对天下的教化理念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措施。以最被近现代诟病的宋代理学的“节孝”观为例,朱元璋在建国伊始,即洪武元年(1368)就颁布了表彰节孝行为的法令,“洪武元年令,今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6]。洪武二十一年(1388)为防止官员敷衍不行奏报,再次榜示天下,广为推行:“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者,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核实入奏。”[7]洪武二十六年(1393)再次强调颁令:“礼部据各处申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理当旌表之人,直隶府州咨都察院,差委监察御史核实,各布政司所属,从按察司核实,着落府州县,同里甲亲邻保勘相同,然后明白奏闻,即行移本处,旌表门闾,以励风俗。”[8]从明初洪武年间颁发的这些法令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于“节孝”的重视与强化。
从历史演变的历程来考察,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仍然持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了强调士大夫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于是对“节孝”观也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尚未能从政治制度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表彰政策。台湾学者费丝言的研究表明:“即使自汉代以降,历代政府皆订有贞节表扬的制度,但就施行状况来看,因‘个例’而制宜的情形仍然相当多。也就是说,在处理上,虽然立有一个大致的模式可供依循,但仍以皇帝的裁示为主要依归;对妇女贞节的奖励,既是国家既定的制度,也是皇帝个别的恩赐。但是,在明代,政府却开始意识到皇帝的施恩于制度运作上可能出现的矛盾,在对请旌的流程与资格加以清楚的规定后,即在政策上维持旌表颁赐的定例,极力降低旌表颁赐因个别恩宠所造成的例外,让旌表的呈请与颁赐得以完全纳入制度中运作。”[9]因此,费丝言把明代以前的政府旌表贞节行为与明代时期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为倡导所致,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旌表制度的运作已完全除去了传统旌表制度中因‘个例’而起的随机性之后,更进一步地常态化为定期的官僚系统作业: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的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10]
与这种政策制度相伴相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国家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清代的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一来,明代政府所推行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于是,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了超越人性、违反人性的激烈化行为。《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且大赞“死得好”的故事[11],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以至有些地方官府也都感到这种胁迫寡妇殉节之风有悖人性而予以示禁。所谓:“民间当妇女不幸夫亡之日,见其跄地呼天、迫不欲生之状,亲族人等苟有人心者,自应恻然动念,从旁劝慰。乃闻闽省有等残忍之徒,或慕殉节虚名,或利寡妇所有,不但不安抚以全其生,反怂恿以速其死。甚或假大义以相责,又或借无倚以迫胁。妇女知识短浅,昏迷之际,惶惑抚措,而丧心病狂之徒,辄为之搭台设祭,并备鼓吹舆从,令本妇盛服登台,亲戚族党皆罗拜活祭,扶掖投缳。此时本妇迫于众论,虽欲不死,不可得矣!似此忍心害理,外假殉节之说,阴图财产之私,胁迫寡妇立致戕生,情固同于威逼,事实等于谋财。……乃愚民陷于不知,自蹈显戮,殊堪怜悯,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所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12]
“孝道”本来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为优秀的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孝道”同样也从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皇帝及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属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天下应该服从于一尊,任何人不可以下犯上。就一般的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是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的。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孝道”,使得背离人性和科学常识的所谓“割股疗亲”行为,大行其道,愈演愈烈。据统计,明清两代,人身上的绝大部分器官,包括眼珠、肝肾、生殖器等等,竟然都有人进行割取来疗亲。[13]为了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不忍睹、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都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下的畸形产物。
从宋代理学对于“节孝”的倡导到明清时期国家政府对于“节孝”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不难看出,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士大夫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到激烈化的歧途。正因为这样,我们通过宋以来跨越王朝断代的历史考察,或许应该对于宋代理学要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解读。
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到了明清时期演化成为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学,这对理学、朱子学本身而言,并不完全是件好事。统治者需要理学、朱子学来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势必对原有的理学、朱子学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没有被实施实践的可能性。朱子学、理学的“义理”“气节”主张,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和爱好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这种经过改造和诠释的“贞节”“孝道”,就不能不与宋代理学家们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距。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反观宋代朱子及理学家们所倡导和坚持的“至理”“人心”等命题,虽然经过历史的长期冲洗,但是它对在尤为纷错之世象变迁中所显现出久远的道德价值,却还是应当引起今天的我们的重视与继承。
二、宋代朱子学、理学的社会组织与礼仪设计及其经世致用
宋明理学研究的哲学化,学者们过分注重理学家们形上思维的“义理”之辩,恰恰又冷落甚至丢失了宋代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的设计与管理的方面。事实上,宋代理学家们所倡导的“理学”,并不完全只是道德与政治的上层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还极力为民间社会的行为礼仪和社会组织进行了新的构建。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社会转型及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平民化”或“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汉唐及之前的诸侯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宗法”世袭体制也分崩离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面对宋代以来这种新的社会重构组合历程,宋代许多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学家们,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对宋代的社会重构和组合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蓝图。这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民间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了。根据冯尔康等先生的研究,宋明时期的宗族、家族制度是从上古时期的“宗法制”演变而来,汉晋时期则演变为门阀士族制度。这种深具统治特权的制度演化至宋代,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基本衰败。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制度成为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大批平民通过科举改变了社会地位。官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以官僚和士绅为主体建立起新的宗族制度。[14]
在唐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宋代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如张载、程颐、程颢、欧阳修、苏洵、范仲淹、司马光、陆九韶等,都积极参与其间,适时地提倡建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
北宋著名的学者张载在论证重建家族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时说:“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15]因此,重新建构家族组织,实行新的“宗法制”,是稳定社会秩序、重树良好社会风俗的必由之路,“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16]。
宋代的社会现实,使家族制度的重建不可能与古代守法制度完全相同,因此,重建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地对古代礼制有所更新。朱熹以其对古代礼制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结合当时的民俗,为宋代社会礼仪特别是重建家族制度设计了新的规范。他在《朱子家礼》的开篇位置,就阐明了建立祠堂的最具创造性的举措。朱熹说:“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17]在倡导敬宗收族的同时,朱熹在《家礼》中对民间社会的诸如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习俗规范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以期社会有所遵行。
朱熹和宋代理学家们的努力,在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张载、程颐、朱熹等人极力倡导的重建民间家族制度和建立祠堂的主张,在宋以后的社会里已经成为推行家族制度的理论依据;欧阳修、苏洵等人创立了民间私家修撰族谱、家乘的样式,为后代所沿袭;《朱子家礼》的设计,至今还在不少地方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宋代所提倡的敬宗收族、义恤乡里以及“义仓”“义学”“义冢”等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我曾经对闽台一带的民间族谱进行过统计分析,朱熹所撰写的族谱序言,至少在30个不同姓氏的族谱中出现过。18]在宋以后的许多民间族谱与相关文献的记载中,时时可见朱熹等宋儒们对于这些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影响,所谓“冠婚丧祭,一如文公《家礼》”,“四时祭飨,略如朱文公所著仪式”。[19]
宋代朱熹等士大夫和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比起他们的“义理”学说来,从宋代开始就显得幸运得多。在他们的设计、倡导以及亲自实践之下,具有一定平民化色彩的新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已经在宋代的许多地方出现。到了元代,平民化的家族制度又有了新的进展,举祠堂之设为例,当时人说:“今也,下达于庶人,通享四代”,[20]“今夫中人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亦莫不思为祖父享祀无穷之计”[21]。一些祭祀始祖及列祖十余世、二十余世以上的大宗祠也不断出现。[22]当然,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于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起,国家政府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延至明朝初期,政府对于民间出现的这种家庙祭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法律上的认可,规定贵族官僚可以建立家庙以祭祀四代祖先,士庶不可立家庙,只能在坟墓旁祭祀两代祖先。嘉靖年间大礼仪之争以后,明朝政府首先允许绅衿建立祠堂、纂修族谱以祭祀祖先。之后,老百姓纷纷效仿,在家中修建祠堂,因此朝廷修改律例,允许百姓修建祠堂祭祀祖先,这一变革逐步演变成为一套有序的、足以维持基层社会稳定平衡的宗族模式。随着民间宗族祭祀制度的确立与扩散,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也日益向民间生活化和民俗化转变。宗族的首要任务是祭祀祖先,繁衍宗族子嗣,在此之外,族产的管理也是宗族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南方地区,宗族通过集体控制财产来维持宗族的祭祀活动,同时也通过对族人招股集资进行商业活动,如进行借贷、扩张田产、经营店铺等,以此来为宗族创造经济利益。[23]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成为中国民间最为重要和坚固的社会结构形式。
到了现当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学者从阶级演变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指摘了不少关于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负面因素,并且预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衰落消亡。我却认为学者们的这种预测未免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出现的两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家族组织和乡族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在许多传统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又一时未能寻找可以与之替代的社会组织的乡村里,普遍出现了一种道德混乱以及社会无序的现象。这两种倾向的出现,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长期存在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文化合理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这种文化合理性,基本上是在宋代理学家们的倡导下,由民间社会自行施行并得以发展兴盛起来的。国家政府不但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甚至在不少的场合加以禁止和干扰。政府往往从强化专制统治的思维出发,认为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壮大,很有可能危及政府的社会治理,从而屡屡试图予以控制和限制。尽管如此,在强大的民间社会面前,这种不具有制度化的控制和限制,毕竟无法有效地影响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以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正是由于较少受到专制政府的制度化约束,宋代理学的这一部分文化精神,被比较正常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基本认同。虽然到了现当代,有一部分学者从政治学术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但是它并没有像被制度化的“节孝”行为那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
宋代朱子学、理学演变到近现代,往往被人们讥讽为迂腐不堪、毫无实用的道德标榜,而注重实用的学人们,对于明清以来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甚为欣赏。实际上,宋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出现的“经世致用”之学,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形上思维,并没有真正实施的内涵与可能性。倒是宋代朱熹及其他理学家们所提倡的重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计与实践,在近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得到全面的实施与推广,甚至延伸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之中。因此,抛开学术与政治上的偏见,如果要在宋以后中国的思想家里寻找真正实施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那么,大概就只能是朱熹等宋儒们的这一主张了。
三、几点认识
从以上对于宋代理学到明清时期演变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近现代以来偏重于哲学化的对于宋代理学的分析,往往把宋代以来的理学引向“形上思维”的文化精神的层面或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忽视了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
2.宋代理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政府的制度化的实践。经历元、明、清时期,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宋代理学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在这制度化的实践推广过程中,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而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
3.被明清时期政府制度化的宋代理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被政府改造过的所谓“气节”观、“节孝”观等,不仅越来越偏离了宋代理学的本意,同时也越来越违背了人性的天真自然以及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了近现代人们的诸多反感。与此相对照的是,宋代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反而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成为真正践行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对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4.从上面的三点认识延伸出来,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说: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儒学,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及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其形成之初,都不乏各自的优秀而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特别是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监督意义,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一旦被社会当政者纳入其制度化的轨道,则必然逐渐沦落为专制统治的附庸角色,从而日益显露出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格。相反,那些没有被专制统治者纳入到政治制度化当中去的儒学传统,则有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合理的本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显示出文化精神的生命力。这种十分粗糙的结论,不妨作为我本人尝试打通宋代以来断代史界限来思考历史问题的一点心得吧。
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容易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为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理学的形而上思维成了哲学家们思考和探究的核心内容,从理学家们的“文本”到研究者们的哲学结论,似乎成了现当代对于理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而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宋代的“思想史”特征,而研究明清史的历史学家们,注重于生长、生活于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各自欣赏、分别陶醉。
21世纪初,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撰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根据夫子自道,他撰写这部著作,就是有鉴于理学的哲学化使它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了家,更和儒学大传统脱了钩。因此,撰写此书,就是“企图从整体的观点将理学放回到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1]《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出版,也正如作者本人所预示的那样,为学术研究“提供另一参照系,使理学的研究逐渐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2]
然而遗憾的是,余英时先生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思考宋代朱熹理学的整体动态的演变过程,还是未能突破断代史的阻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们,固然全力重新建构“政治文化”与自身“内圣”修养的尊严而可贵的“道统”,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种尊严而可贵的“道统”,确确实实给后世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正是这些负面的影响,让现当代许多思想敏锐的学者们,产生了对“理学”弃之而后快的激愤心态。那么,从宋代到近现代,这中间即明清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好奇和思考。而这种思考,无疑应该首先打破断代史的人为阻隔,从长时段的演变历史来解读这一“理学”过程,或许是相当有益的事情。
一、宋代以来朱子学、理学的政治制度化变迁
宋代的理学家们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设计了深具儒家传统的道德标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试图把这些道德标准实践于现实政治、社会与个人。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宋代理学家们所设计的这些道德标准,基本上没有在宋代形成制度化的实践。这种制度化的实践,经历了元、明时期的不断演化。
元朝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华,亟须借助汉人的道统来稳定统治、治理天下,因此从忽必烈即位之后,就“大召名儒,辟广庠序”,修造孔庙,翻译和学习儒家经籍。其中兴学校之举,影响至巨。在许衡、耶律有尚等人的推动下,宋代朱熹等人所倡导的教育体制,在元代得到了实行。“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3]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学校,所教皆朱子之书。[4]元朝以朱子理学为知识范本的教育体制的推行,对于明清时期朱子学、理学演化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起到了过渡桥梁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实施,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有制度上的推行与保障。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后,以恢复汉官威仪为己任,宋代的道德标准自然成了恢复汉官威仪的最直接和最可行的政治、社会范本。于是,科举制度的重建,就自然而然地沿袭元代的理念,虽然说“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他起兵反元的鲜明口号,但是要想稳定统治,特别是官僚队伍的培养,就不能不追随于元朝之后,把宋代理学家们特别是朱熹的著作,确定为学子们进身仕途的必读、必考法定教科书。[5]换言之,朱熹等宋儒们的道德主张,很快占据着明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
为了强化这一意识形态,朱元璋还对天下的教化理念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措施。以最被近现代诟病的宋代理学的“节孝”观为例,朱元璋在建国伊始,即洪武元年(1368)就颁布了表彰节孝行为的法令,“洪武元年令,今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6]。洪武二十一年(1388)为防止官员敷衍不行奏报,再次榜示天下,广为推行:“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者,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核实入奏。”[7]洪武二十六年(1393)再次强调颁令:“礼部据各处申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理当旌表之人,直隶府州咨都察院,差委监察御史核实,各布政司所属,从按察司核实,着落府州县,同里甲亲邻保勘相同,然后明白奏闻,即行移本处,旌表门闾,以励风俗。”[8]从明初洪武年间颁发的这些法令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于“节孝”的重视与强化。
从历史演变的历程来考察,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仍然持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了强调士大夫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于是对“节孝”观也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尚未能从政治制度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表彰政策。台湾学者费丝言的研究表明:“即使自汉代以降,历代政府皆订有贞节表扬的制度,但就施行状况来看,因‘个例’而制宜的情形仍然相当多。也就是说,在处理上,虽然立有一个大致的模式可供依循,但仍以皇帝的裁示为主要依归;对妇女贞节的奖励,既是国家既定的制度,也是皇帝个别的恩赐。但是,在明代,政府却开始意识到皇帝的施恩于制度运作上可能出现的矛盾,在对请旌的流程与资格加以清楚的规定后,即在政策上维持旌表颁赐的定例,极力降低旌表颁赐因个别恩宠所造成的例外,让旌表的呈请与颁赐得以完全纳入制度中运作。”[9]因此,费丝言把明代以前的政府旌表贞节行为与明代时期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为倡导所致,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旌表制度的运作已完全除去了传统旌表制度中因‘个例’而起的随机性之后,更进一步地常态化为定期的官僚系统作业: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的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10]
与这种政策制度相伴相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国家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清代的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一来,明代政府所推行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于是,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了超越人性、违反人性的激烈化行为。《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且大赞“死得好”的故事[11],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以至有些地方官府也都感到这种胁迫寡妇殉节之风有悖人性而予以示禁。所谓:“民间当妇女不幸夫亡之日,见其跄地呼天、迫不欲生之状,亲族人等苟有人心者,自应恻然动念,从旁劝慰。乃闻闽省有等残忍之徒,或慕殉节虚名,或利寡妇所有,不但不安抚以全其生,反怂恿以速其死。甚或假大义以相责,又或借无倚以迫胁。妇女知识短浅,昏迷之际,惶惑抚措,而丧心病狂之徒,辄为之搭台设祭,并备鼓吹舆从,令本妇盛服登台,亲戚族党皆罗拜活祭,扶掖投缳。此时本妇迫于众论,虽欲不死,不可得矣!似此忍心害理,外假殉节之说,阴图财产之私,胁迫寡妇立致戕生,情固同于威逼,事实等于谋财。……乃愚民陷于不知,自蹈显戮,殊堪怜悯,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所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12]
“孝道”本来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为优秀的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孝道”同样也从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皇帝及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属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天下应该服从于一尊,任何人不可以下犯上。就一般的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是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的。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孝道”,使得背离人性和科学常识的所谓“割股疗亲”行为,大行其道,愈演愈烈。据统计,明清两代,人身上的绝大部分器官,包括眼珠、肝肾、生殖器等等,竟然都有人进行割取来疗亲。[13]为了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不忍睹、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都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下的畸形产物。
从宋代理学对于“节孝”的倡导到明清时期国家政府对于“节孝”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不难看出,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士大夫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到激烈化的歧途。正因为这样,我们通过宋以来跨越王朝断代的历史考察,或许应该对于宋代理学要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解读。
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到了明清时期演化成为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学,这对理学、朱子学本身而言,并不完全是件好事。统治者需要理学、朱子学来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势必对原有的理学、朱子学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没有被实施实践的可能性。朱子学、理学的“义理”“气节”主张,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和爱好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这种经过改造和诠释的“贞节”“孝道”,就不能不与宋代理学家们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距。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反观宋代朱子及理学家们所倡导和坚持的“至理”“人心”等命题,虽然经过历史的长期冲洗,但是它对在尤为纷错之世象变迁中所显现出久远的道德价值,却还是应当引起今天的我们的重视与继承。
二、宋代朱子学、理学的社会组织与礼仪设计及其经世致用
宋明理学研究的哲学化,学者们过分注重理学家们形上思维的“义理”之辩,恰恰又冷落甚至丢失了宋代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的设计与管理的方面。事实上,宋代理学家们所倡导的“理学”,并不完全只是道德与政治的上层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还极力为民间社会的行为礼仪和社会组织进行了新的构建。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社会转型及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平民化”或“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汉唐及之前的诸侯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宗法”世袭体制也分崩离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面对宋代以来这种新的社会重构组合历程,宋代许多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学家们,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对宋代的社会重构和组合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蓝图。这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民间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了。根据冯尔康等先生的研究,宋明时期的宗族、家族制度是从上古时期的“宗法制”演变而来,汉晋时期则演变为门阀士族制度。这种深具统治特权的制度演化至宋代,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基本衰败。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制度成为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大批平民通过科举改变了社会地位。官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以官僚和士绅为主体建立起新的宗族制度。[14]
在唐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宋代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如张载、程颐、程颢、欧阳修、苏洵、范仲淹、司马光、陆九韶等,都积极参与其间,适时地提倡建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
北宋著名的学者张载在论证重建家族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时说:“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15]因此,重新建构家族组织,实行新的“宗法制”,是稳定社会秩序、重树良好社会风俗的必由之路,“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16]。
宋代的社会现实,使家族制度的重建不可能与古代守法制度完全相同,因此,重建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地对古代礼制有所更新。朱熹以其对古代礼制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结合当时的民俗,为宋代社会礼仪特别是重建家族制度设计了新的规范。他在《朱子家礼》的开篇位置,就阐明了建立祠堂的最具创造性的举措。朱熹说:“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17]在倡导敬宗收族的同时,朱熹在《家礼》中对民间社会的诸如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习俗规范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以期社会有所遵行。
朱熹和宋代理学家们的努力,在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张载、程颐、朱熹等人极力倡导的重建民间家族制度和建立祠堂的主张,在宋以后的社会里已经成为推行家族制度的理论依据;欧阳修、苏洵等人创立了民间私家修撰族谱、家乘的样式,为后代所沿袭;《朱子家礼》的设计,至今还在不少地方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宋代所提倡的敬宗收族、义恤乡里以及“义仓”“义学”“义冢”等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我曾经对闽台一带的民间族谱进行过统计分析,朱熹所撰写的族谱序言,至少在30个不同姓氏的族谱中出现过。18]在宋以后的许多民间族谱与相关文献的记载中,时时可见朱熹等宋儒们对于这些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影响,所谓“冠婚丧祭,一如文公《家礼》”,“四时祭飨,略如朱文公所著仪式”。[19]
宋代朱熹等士大夫和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比起他们的“义理”学说来,从宋代开始就显得幸运得多。在他们的设计、倡导以及亲自实践之下,具有一定平民化色彩的新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已经在宋代的许多地方出现。到了元代,平民化的家族制度又有了新的进展,举祠堂之设为例,当时人说:“今也,下达于庶人,通享四代”,[20]“今夫中人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亦莫不思为祖父享祀无穷之计”[21]。一些祭祀始祖及列祖十余世、二十余世以上的大宗祠也不断出现。[22]当然,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于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起,国家政府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延至明朝初期,政府对于民间出现的这种家庙祭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法律上的认可,规定贵族官僚可以建立家庙以祭祀四代祖先,士庶不可立家庙,只能在坟墓旁祭祀两代祖先。嘉靖年间大礼仪之争以后,明朝政府首先允许绅衿建立祠堂、纂修族谱以祭祀祖先。之后,老百姓纷纷效仿,在家中修建祠堂,因此朝廷修改律例,允许百姓修建祠堂祭祀祖先,这一变革逐步演变成为一套有序的、足以维持基层社会稳定平衡的宗族模式。随着民间宗族祭祀制度的确立与扩散,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也日益向民间生活化和民俗化转变。宗族的首要任务是祭祀祖先,繁衍宗族子嗣,在此之外,族产的管理也是宗族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南方地区,宗族通过集体控制财产来维持宗族的祭祀活动,同时也通过对族人招股集资进行商业活动,如进行借贷、扩张田产、经营店铺等,以此来为宗族创造经济利益。[23]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成为中国民间最为重要和坚固的社会结构形式。
到了现当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学者从阶级演变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指摘了不少关于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负面因素,并且预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衰落消亡。我却认为学者们的这种预测未免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出现的两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家族组织和乡族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在许多传统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又一时未能寻找可以与之替代的社会组织的乡村里,普遍出现了一种道德混乱以及社会无序的现象。这两种倾向的出现,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长期存在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文化合理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这种文化合理性,基本上是在宋代理学家们的倡导下,由民间社会自行施行并得以发展兴盛起来的。国家政府不但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甚至在不少的场合加以禁止和干扰。政府往往从强化专制统治的思维出发,认为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壮大,很有可能危及政府的社会治理,从而屡屡试图予以控制和限制。尽管如此,在强大的民间社会面前,这种不具有制度化的控制和限制,毕竟无法有效地影响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以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正是由于较少受到专制政府的制度化约束,宋代理学的这一部分文化精神,被比较正常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基本认同。虽然到了现当代,有一部分学者从政治学术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但是它并没有像被制度化的“节孝”行为那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
宋代朱子学、理学演变到近现代,往往被人们讥讽为迂腐不堪、毫无实用的道德标榜,而注重实用的学人们,对于明清以来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甚为欣赏。实际上,宋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出现的“经世致用”之学,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形上思维,并没有真正实施的内涵与可能性。倒是宋代朱熹及其他理学家们所提倡的重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计与实践,在近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得到全面的实施与推广,甚至延伸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之中。因此,抛开学术与政治上的偏见,如果要在宋以后中国的思想家里寻找真正实施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那么,大概就只能是朱熹等宋儒们的这一主张了。
三、几点认识
从以上对于宋代理学到明清时期演变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近现代以来偏重于哲学化的对于宋代理学的分析,往往把宋代以来的理学引向“形上思维”的文化精神的层面或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忽视了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
2.宋代理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政府的制度化的实践。经历元、明、清时期,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宋代理学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在这制度化的实践推广过程中,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而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
3.被明清时期政府制度化的宋代理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被政府改造过的所谓“气节”观、“节孝”观等,不仅越来越偏离了宋代理学的本意,同时也越来越违背了人性的天真自然以及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了近现代人们的诸多反感。与此相对照的是,宋代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反而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成为真正践行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对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4.从上面的三点认识延伸出来,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说: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儒学,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及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其形成之初,都不乏各自的优秀而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特别是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监督意义,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一旦被社会当政者纳入其制度化的轨道,则必然逐渐沦落为专制统治的附庸角色,从而日益显露出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格。相反,那些没有被专制统治者纳入到政治制度化当中去的儒学传统,则有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合理的本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显示出文化精神的生命力。这种十分粗糙的结论,不妨作为我本人尝试打通宋代以来断代史界限来思考历史问题的一点心得吧。
附注
注释: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总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页。
[2]同上。
[3]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邵氏义塾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4]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8页。
[5]《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6](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七十九《旌表》,台北:文海出版社。
[7]同上。
[8]同上。
[9]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辩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 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年,第113页。
[10]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辩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第一章《明代国家贞节表扬制度》,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年。
[11]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
[12]《福建省例》三十四《杂例·禁止殉烈》,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
[13]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考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年。
[14]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16]同上。
[17]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祠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8]陈支平:《福建族谱》第五章《族谱的装饰与炫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
[19]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177页。
[20]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六《豫章甘氏祠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1]李祁:《云阳集》卷七《汪氏永思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2]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177页。
[23]科大卫著,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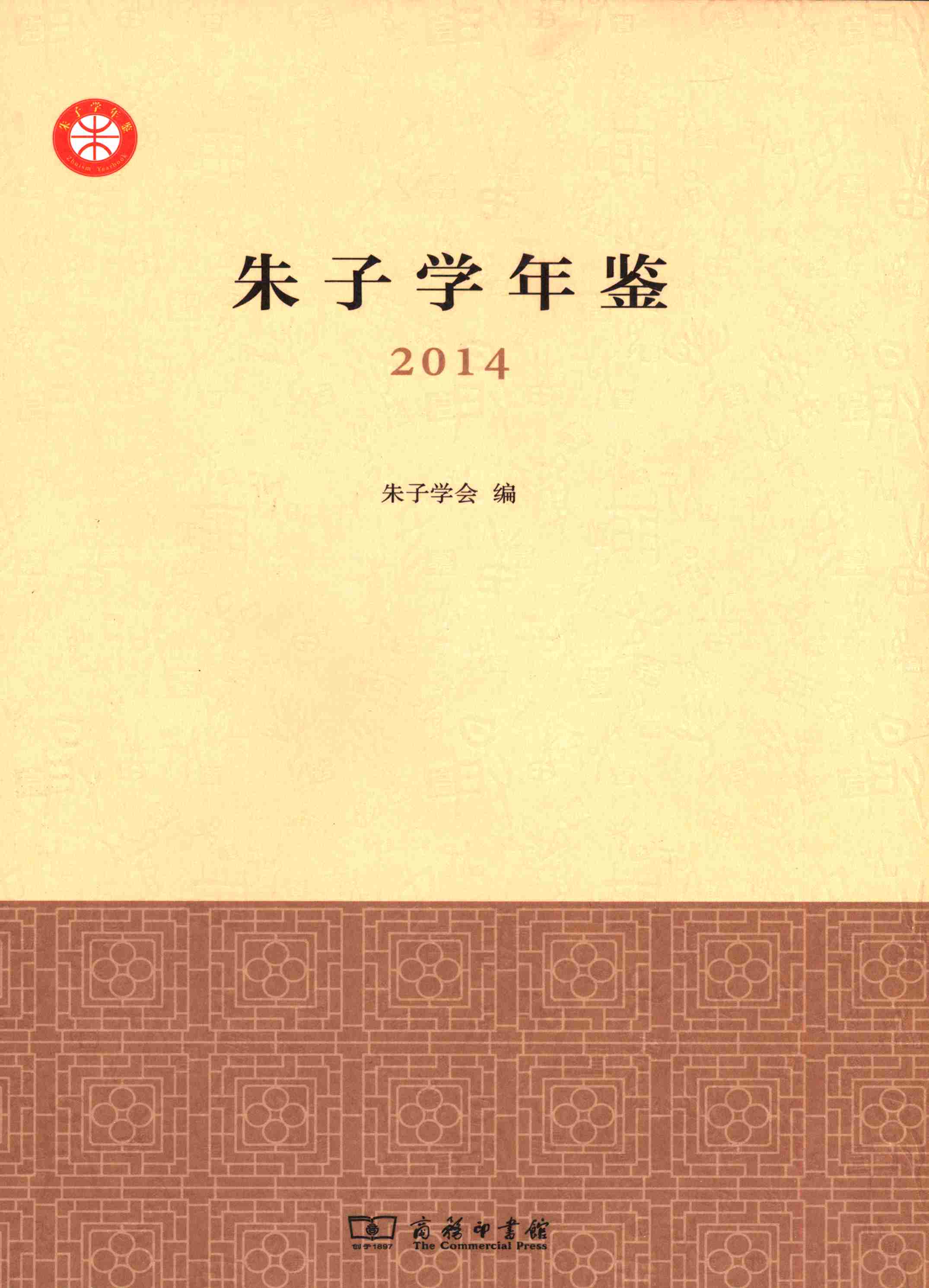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4》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分为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等九个栏目,收录了《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支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