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与统合主客观世界的人本智慧之学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4》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677 |
| 颗粒名称: | 二、认识与统合主客观世界的人本智慧之学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5 |
| 页码: | 028-03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的哲学中,理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净洁空阔的世界,但它并不能脱离与逻辑结构的关系。理必须通过一个实体来实现,而这个实体就是气。气是理的承载和运动的载体,通过气的运动,哲学逻辑结构得以展开聚散、造作、发展等活动。通过气与理的冲突、融合以及气自身的变化和理气的运动,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具有生命力和辩证思维。 |
| 关键词: | 朱熹思想 价值 朱子学 |
内容
尽管理作为其哲学形上学的核心范畴是无造作、无计度、无情意的,是一个纯然绝对、净洁空阔的世界,但不能真正脱离逻辑结构的关系。
因为理作为“净洁空阔的世界”,必须落实在一个“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是气,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由气使其哲学逻辑结构得以展开聚散、造作、发育流行等活动;由气与理的冲突、融合以及气自身动静变化及理气的“理一分殊”运动,使朱熹哲学逻辑结构具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和辩证思维。
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本体,或称根底。“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5]“本乎一源”的源,即是理,是万物的根底。
理与气、与物既不离,又不杂。从不离说,一方面体认理,必须通过“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使物与理之间保持沟通、会通,消除其间的闭塞;另一方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与物都蕴含着理,人物不离理。从不杂说,“净洁空阔世界”的理,超越人与物。“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6]形上的理是无形无影的,人与物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的。理在逻辑上是先在的、超越的,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
形而上的理,依傍气而化生万物。在化生万物以后,如何由物而体认形而上的理,即由物返归理,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觉、心思、知行等范畴,并以此开展其哲学逻辑结构的体认活动。
朱熹冲决了唐以来“疏不破注”的网罗,敢于改经补经,而作“格物致知补传”。他明言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人心有知,天下的万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是因为知有未尽。“即物穷理”而到极尽处,众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的大用就明白了。格物而获致知的途径是“合内外之理”的过程,即主体人心(内)与客体事物(外)的融合。
格物的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并不是存心于一草一木之间。穷理是涵养本原的功夫,持敬是穷理的根本。“致知”的“致”是推致的意思,即推致我心的知识,以达到全知。格物致知,并不是把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格到,都知会。即使有一二件事不知道,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亦可“识得他破”,“通将去”。类推是由近而远,逐渐理会;由浅入深,层层而进;由粗到精,无所不尽。这样理会多了,便能“自然脱然有悟处”,即对理的觉悟。
持敬是穷理的根本。穷理的要旨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贵于循序而进,达于致精微。致精微的根本在于居敬持志,只有居敬,才能穷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均蕴含着知与行的关系。程颐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认为,程颐是把知与行做“两脚说”。只要把知行分先后,那么,必知先行后。譬如人走路,只有知路如何走,才会走到目的地。知得才能行得,行必依赖于知。若论“知行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即“知轻行重”,注重践行。这是从知的成果上说的。朱熹之所以注重践行,是出于对《尚书》思想的继承。“《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7]行是明理之终,是检验知真不真的标准。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
朱熹既体认到知行互相区别,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又认识到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8]相须,即互相联结、依赖。
格物、即物,物从哪里来?气作为理的“生物之具”,是不可或缺的。“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9]此“散”字是“理一分殊”的分的意思。理一的“一”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本体理,是万殊、阴阳形而上的根据。凡事物都具有对待性的两端,其内与外也具有相对性。“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10]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阴阳,阳中有阴阳;男女各自有阴阳。这就构成对待的普遍性、无限性。
阳为动,阴为静。由于阴阳具有普遍性、无限性,动静便亦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11]即是说他否定运动与静止有端始,而把其看作无限的过程,动静具有相关性、循环性。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动静有端始,是一种割裂动静的思维作怪,是其认知上的局限所致。
朱熹从动静普遍性、无限性出发,提出了运动的化与变两种形态:“化是渐化,变是顿变,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难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固是如此。”[12]渐化是月变、日变、时变,是不被人知觉的、不显著的变化;是渐渐消磨去,如树木渐长,不是突然变化;是无痕迹的变化,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由这些规定可知,其所谓渐化,犹当今所说的量变。渐化在一定限度内,事物仍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内涵和形态;但渐化超出了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变,朱熹称之为顿变。它是一种倏忽、突然的顿变;是显著的、有头面可见的变;顿变是渐化的截断。
朱熹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其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是经学,其诠释的依傍文本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宋代经学超越汉唐,变革古训,进而开出新学风。宋儒以无畏精神解放思想,冲决“五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罗,破除“家法”“师法”的迷信,直接孔孟,以唤回儒学的真精神。朱熹以理体学新思维、以“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诠释经典,重开生命智慧,重建性命道德,重构精神家园。他以“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通经致用,道器一源,理一分殊,体现了宋学经典诠释的真精神。
朱熹以毕生心血注解和研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及“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熹所首创。中国哲学是一开放的体系,每一新学术思潮的诞生,思维形态的转生,核心话题的转换,与其相应地导致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的变换。理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其人文语境是纲常和价值理想的重建;其诠释文本是“四书”,这是理学理论思维形态建构的支柱。
朱熹对《论语》创造性的诠释,表现为无处不以理、天理来解读其义理。如释“仁”为“爱之理”;释“礼”为“天理之节文”;释“朝闻道”的“道”为“事物当然之理”;释“吾道一以贯之”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释“君子喻于义”的“义”为“天理之所宜”;释“性与天道”为“其实一理也”,等等。他把《论语》中的重要概念,都依据自己的理体学思想予以解读,体现了理学的时代精神。虽然这并不一定符合《论语》文本的原意,却赋予《论语》以适应时代的新价值、新生命,变《论语》为朱熹时代的《论语》,使之成为发挥朱熹理体学思想的《论语》,即化旧学为新知。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尊孟思想,对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和郑厚的《艺圃折衷》,逐条予以辨正。他认为孟子乃是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当的人,以批驳以往诽孟的种种言论。认为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孟子辟杨墨,距诐行,放淫辞,使邪说不作,明正道,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强调了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熹自谓“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大学》)”,“某于《大学》用工甚多”。[13]据载,他去世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他之所以注重《大学》,乃是认为其是人之为学的“大坯模”,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概括了修己治人之道,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且从内圣的格致、诚意、正心出发,通过修身,而开出外王的齐、治、平。这是朱熹理体学建构所不可或缺的基石。
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他之所以推崇《中庸》,乃是因为忧道学之失传。程朱继孔孟之道统,揭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遂成为尧、舜、禹、汤至孔、孟的“传授心法”。他将之作为理学“内圣”的要旨,以发明道统。他对《中庸》的分章,是其依理体学理论思维的体认和诠释。
“四书”的编成,使理学学术思潮的理论体系有了依傍经典文本的支撑,使理学思潮的在世发展有了合理性的依据。
朱熹于“四书”用心最多,同时对其他经典亦予以精心的诠释。他是宋易的集大成者,于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经其钻研后,剥去其圣人之言的光环,确定其为卜筮之书的性质。他以理体学为指导,融合义理、图书、象数、卜筮之学。他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二是交易。此两义都以阴阳为着眼点。从阴阳之理说,它是阴阳所以的形上之体;从阴阳之事说,它是形而下之用。
至于“尚书学”,朱熹无专著,然辨伪《古文尚书》为晚出,孔安国的《尚书传》,亦恐是魏晋人所作。他筚路蓝缕,开明清辨伪之端,并指导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
朱熹从20岁开始研究《诗经》,到48岁撰成《诗集传》,他始宗《诗序》,后弃《诗序》,认为《诗序》为后人妄意推想诗人的美刺,不是古人所作,所以不能以《诗序》为证来诠释、理解《诗》的本义。他把诗定义为“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14],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流出。他进而否定了孔子“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教条,认为诗作并非都无邪,而是既然有善,亦有淫邪、淫奔之诗。这是宋代掀起“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表征,标志着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化。
在“礼学”方面,朱熹重礼,早年作《祭礼》《家礼》,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未完成而卒,由其学生续成)。他以《周礼》为纲领,认为“《周礼》规模皆是周公作”,“大纲却是周公意思”。[15]《仪礼》不是古人预先作的,而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再由圣人加以筛选和改进,而编成《仪礼》一书。他认为《礼记》要兼《仪礼》来读,《仪礼》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致使许多礼皆无安著的地方。他从义理层面释《礼记》,以体现理体学的理论思维生命的源泉。
朱熹阐述《春秋》大义,认为体认圣人意蕴,如果在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则是舍本求末;其大义就在于明道正宜,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夷狄。这是《春秋》的大旨,亦是天理所至。他批评一些人以自己的利欲之心诠释《春秋》,揣度圣人之意,属于一种巧说曲解,不符合《春秋》大义本旨。他认为圣人此书之作,是为了遏人欲于横流。遏人欲,是为了存天理。《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史学,《公羊传》《穀梁传》为经学,史学记事详,讲道理差;《公》《穀》于义理上有功,于记事上多误。
朱熹释经,重义理,但并不排斥章句训诂之学。他兼综汉宋,开诠释经典之新风;经传二分,通经求理。“分”以直接体贴经文意蕴;只有不受传统的束缚,才能体认经文本身的义理。“通”以敞开门户,在互相沟通、交感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求索其理。朱熹诠释经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诠释方法、逻辑结构,对经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因为理作为“净洁空阔的世界”,必须落实在一个“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是气,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由气使其哲学逻辑结构得以展开聚散、造作、发育流行等活动;由气与理的冲突、融合以及气自身动静变化及理气的“理一分殊”运动,使朱熹哲学逻辑结构具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和辩证思维。
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本体,或称根底。“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5]“本乎一源”的源,即是理,是万物的根底。
理与气、与物既不离,又不杂。从不离说,一方面体认理,必须通过“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使物与理之间保持沟通、会通,消除其间的闭塞;另一方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与物都蕴含着理,人物不离理。从不杂说,“净洁空阔世界”的理,超越人与物。“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6]形上的理是无形无影的,人与物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的。理在逻辑上是先在的、超越的,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
形而上的理,依傍气而化生万物。在化生万物以后,如何由物而体认形而上的理,即由物返归理,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觉、心思、知行等范畴,并以此开展其哲学逻辑结构的体认活动。
朱熹冲决了唐以来“疏不破注”的网罗,敢于改经补经,而作“格物致知补传”。他明言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人心有知,天下的万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是因为知有未尽。“即物穷理”而到极尽处,众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的大用就明白了。格物而获致知的途径是“合内外之理”的过程,即主体人心(内)与客体事物(外)的融合。
格物的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并不是存心于一草一木之间。穷理是涵养本原的功夫,持敬是穷理的根本。“致知”的“致”是推致的意思,即推致我心的知识,以达到全知。格物致知,并不是把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格到,都知会。即使有一二件事不知道,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亦可“识得他破”,“通将去”。类推是由近而远,逐渐理会;由浅入深,层层而进;由粗到精,无所不尽。这样理会多了,便能“自然脱然有悟处”,即对理的觉悟。
持敬是穷理的根本。穷理的要旨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贵于循序而进,达于致精微。致精微的根本在于居敬持志,只有居敬,才能穷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均蕴含着知与行的关系。程颐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认为,程颐是把知与行做“两脚说”。只要把知行分先后,那么,必知先行后。譬如人走路,只有知路如何走,才会走到目的地。知得才能行得,行必依赖于知。若论“知行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即“知轻行重”,注重践行。这是从知的成果上说的。朱熹之所以注重践行,是出于对《尚书》思想的继承。“《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7]行是明理之终,是检验知真不真的标准。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
朱熹既体认到知行互相区别,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又认识到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8]相须,即互相联结、依赖。
格物、即物,物从哪里来?气作为理的“生物之具”,是不可或缺的。“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9]此“散”字是“理一分殊”的分的意思。理一的“一”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本体理,是万殊、阴阳形而上的根据。凡事物都具有对待性的两端,其内与外也具有相对性。“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10]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阴阳,阳中有阴阳;男女各自有阴阳。这就构成对待的普遍性、无限性。
阳为动,阴为静。由于阴阳具有普遍性、无限性,动静便亦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11]即是说他否定运动与静止有端始,而把其看作无限的过程,动静具有相关性、循环性。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动静有端始,是一种割裂动静的思维作怪,是其认知上的局限所致。
朱熹从动静普遍性、无限性出发,提出了运动的化与变两种形态:“化是渐化,变是顿变,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难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固是如此。”[12]渐化是月变、日变、时变,是不被人知觉的、不显著的变化;是渐渐消磨去,如树木渐长,不是突然变化;是无痕迹的变化,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由这些规定可知,其所谓渐化,犹当今所说的量变。渐化在一定限度内,事物仍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内涵和形态;但渐化超出了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变,朱熹称之为顿变。它是一种倏忽、突然的顿变;是显著的、有头面可见的变;顿变是渐化的截断。
朱熹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其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是经学,其诠释的依傍文本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宋代经学超越汉唐,变革古训,进而开出新学风。宋儒以无畏精神解放思想,冲决“五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罗,破除“家法”“师法”的迷信,直接孔孟,以唤回儒学的真精神。朱熹以理体学新思维、以“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诠释经典,重开生命智慧,重建性命道德,重构精神家园。他以“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通经致用,道器一源,理一分殊,体现了宋学经典诠释的真精神。
朱熹以毕生心血注解和研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及“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熹所首创。中国哲学是一开放的体系,每一新学术思潮的诞生,思维形态的转生,核心话题的转换,与其相应地导致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的变换。理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其人文语境是纲常和价值理想的重建;其诠释文本是“四书”,这是理学理论思维形态建构的支柱。
朱熹对《论语》创造性的诠释,表现为无处不以理、天理来解读其义理。如释“仁”为“爱之理”;释“礼”为“天理之节文”;释“朝闻道”的“道”为“事物当然之理”;释“吾道一以贯之”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释“君子喻于义”的“义”为“天理之所宜”;释“性与天道”为“其实一理也”,等等。他把《论语》中的重要概念,都依据自己的理体学思想予以解读,体现了理学的时代精神。虽然这并不一定符合《论语》文本的原意,却赋予《论语》以适应时代的新价值、新生命,变《论语》为朱熹时代的《论语》,使之成为发挥朱熹理体学思想的《论语》,即化旧学为新知。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尊孟思想,对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和郑厚的《艺圃折衷》,逐条予以辨正。他认为孟子乃是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当的人,以批驳以往诽孟的种种言论。认为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孟子辟杨墨,距诐行,放淫辞,使邪说不作,明正道,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强调了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熹自谓“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大学》)”,“某于《大学》用工甚多”。[13]据载,他去世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他之所以注重《大学》,乃是认为其是人之为学的“大坯模”,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概括了修己治人之道,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且从内圣的格致、诚意、正心出发,通过修身,而开出外王的齐、治、平。这是朱熹理体学建构所不可或缺的基石。
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他之所以推崇《中庸》,乃是因为忧道学之失传。程朱继孔孟之道统,揭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遂成为尧、舜、禹、汤至孔、孟的“传授心法”。他将之作为理学“内圣”的要旨,以发明道统。他对《中庸》的分章,是其依理体学理论思维的体认和诠释。
“四书”的编成,使理学学术思潮的理论体系有了依傍经典文本的支撑,使理学思潮的在世发展有了合理性的依据。
朱熹于“四书”用心最多,同时对其他经典亦予以精心的诠释。他是宋易的集大成者,于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经其钻研后,剥去其圣人之言的光环,确定其为卜筮之书的性质。他以理体学为指导,融合义理、图书、象数、卜筮之学。他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二是交易。此两义都以阴阳为着眼点。从阴阳之理说,它是阴阳所以的形上之体;从阴阳之事说,它是形而下之用。
至于“尚书学”,朱熹无专著,然辨伪《古文尚书》为晚出,孔安国的《尚书传》,亦恐是魏晋人所作。他筚路蓝缕,开明清辨伪之端,并指导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
朱熹从20岁开始研究《诗经》,到48岁撰成《诗集传》,他始宗《诗序》,后弃《诗序》,认为《诗序》为后人妄意推想诗人的美刺,不是古人所作,所以不能以《诗序》为证来诠释、理解《诗》的本义。他把诗定义为“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14],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流出。他进而否定了孔子“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教条,认为诗作并非都无邪,而是既然有善,亦有淫邪、淫奔之诗。这是宋代掀起“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表征,标志着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化。
在“礼学”方面,朱熹重礼,早年作《祭礼》《家礼》,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未完成而卒,由其学生续成)。他以《周礼》为纲领,认为“《周礼》规模皆是周公作”,“大纲却是周公意思”。[15]《仪礼》不是古人预先作的,而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再由圣人加以筛选和改进,而编成《仪礼》一书。他认为《礼记》要兼《仪礼》来读,《仪礼》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致使许多礼皆无安著的地方。他从义理层面释《礼记》,以体现理体学的理论思维生命的源泉。
朱熹阐述《春秋》大义,认为体认圣人意蕴,如果在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则是舍本求末;其大义就在于明道正宜,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夷狄。这是《春秋》的大旨,亦是天理所至。他批评一些人以自己的利欲之心诠释《春秋》,揣度圣人之意,属于一种巧说曲解,不符合《春秋》大义本旨。他认为圣人此书之作,是为了遏人欲于横流。遏人欲,是为了存天理。《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史学,《公羊传》《穀梁传》为经学,史学记事详,讲道理差;《公》《穀》于义理上有功,于记事上多误。
朱熹释经,重义理,但并不排斥章句训诂之学。他兼综汉宋,开诠释经典之新风;经传二分,通经求理。“分”以直接体贴经文意蕴;只有不受传统的束缚,才能体认经文本身的义理。“通”以敞开门户,在互相沟通、交感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求索其理。朱熹诠释经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诠释方法、逻辑结构,对经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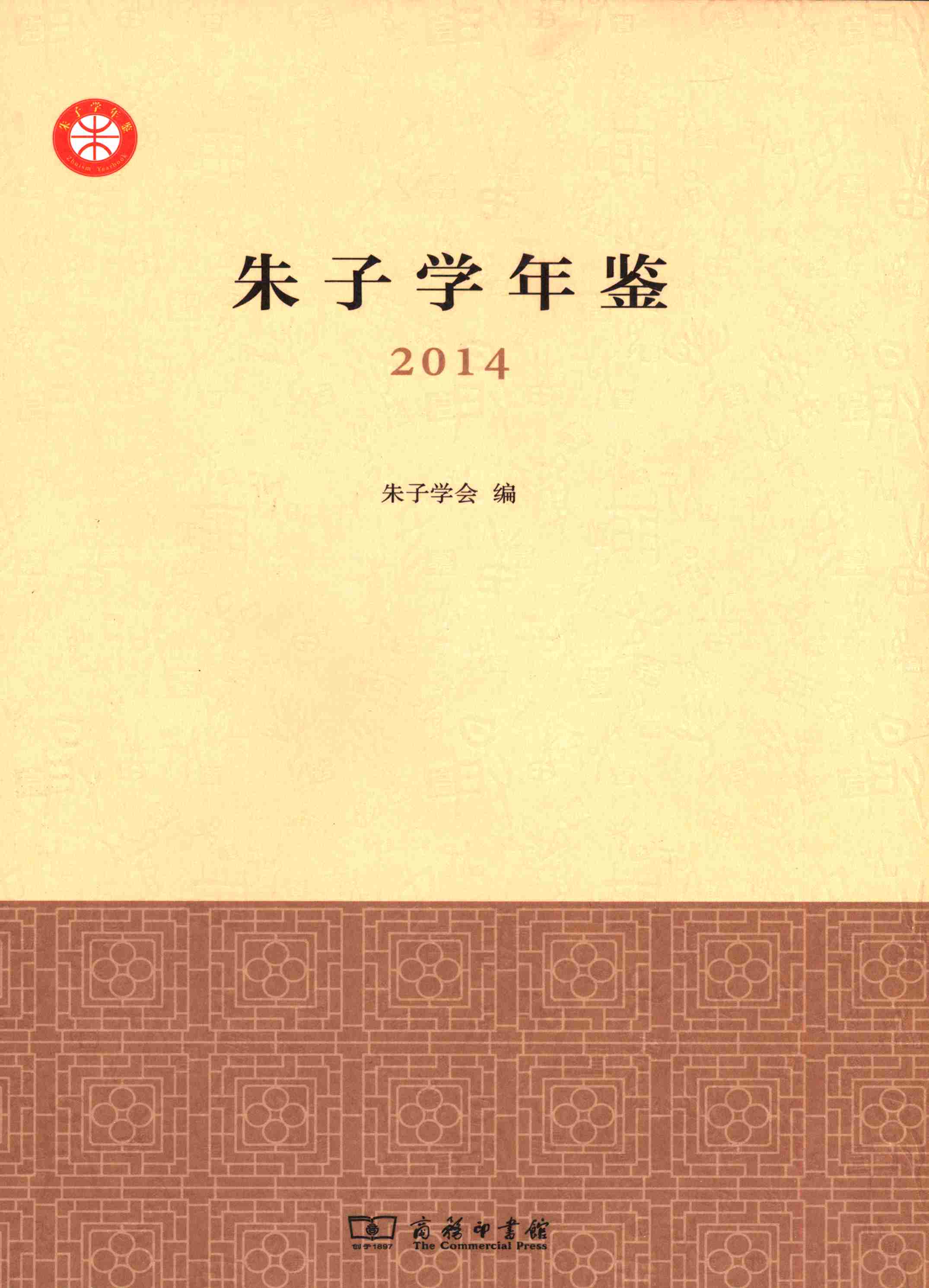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4》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分为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等九个栏目,收录了《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张立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