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新知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4》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675 |
| 颗粒名称: | 旧学新知 |
| 其他题名: | 朱熹思想及其价值综论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10-03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心灵体验凝练成许多有启迪意义的话语和诗词,这些思想在古代世界文化中具有广泛影响。朱熹强调理学思想的实践性和转化能力,将古代学说转化为新知识,将深邃的学问转化为实践行动。我们需要将古代哲学思想与现代价值相结合,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实践探索,从而使古代智慧焕发新的生命力。 |
| 关键词: | 朱熹思想 价值 朱子学 |
内容
朱熹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几千年中华文明薪火的传承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子学被东亚一些国家尊奉为意识形态,在古代世界文化思想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朱熹将其生命的体验、坎坷的经历、求道的实践、心灵的觉解,凝练成扣人心弦、激动人情、启迪人生、化解冲突、追求和合的诸多话语、箴言、警句、诗词。尽管时代屡迁,但它们像闪光的金子,不减其辉煌,在当前可化旧为新、化死为活、化古为今、化丑为美、化恶为善,即化腐朽为神奇。“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进而言之,转旧学为新知,探邃密为深沉,化学理为实践,这不但是朱熹治学的根本之道,更应成为我们批判体用中国古代思想智慧(包括朱熹的理学思想)、造益现代化事业的理性态度。
中华文化注重笃行,主张知行合一。任何思想与理论如果不能转化为行动,则不啻为空谈。尤其是对于古代哲学乃至人文思想而言,我们现今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的当务之急,乃是对之进行与时偕行、囊括古今中外成果和全人类智慧的思想内容集成、批判性扬弃、时代价值阐发、社会人文意义掘析、应用路径探究和实践性体用转化;如此方能真正使之通过不断推陈出新和与时偕行而得以实现其人本性的价值转化:代代生根发芽、辈辈开花结果,借此方能永葆国学精神和民族思想智慧之永久生机。从广义和终极角度而言,人心之用和人体之用,乃是一切人文思想及理论的根本目标所在、根本价值的体现和生命活力的无尽源泉所在。
一、造益古代政治经济的理性观念
洞悉天理,这是朱熹思想哲学的核心话题,是其政治、经济、哲学、经学、美学、道德、教育等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理(天理)在朱熹的思想逻辑体系中,是形而上本体。“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1]理是亘古亘今,常存不灭,超越人物生灭的无限,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根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2]。天地人及其性,都以理为所以然者,以理为终极的根源。
由此,政治为天理政治,变以往“君权神授”为“天理君权”,革“天授君权”为“理授君权”,但他不完全否定天威,仍以天威来劝诫、约束君威、君权,使之不过分膨胀,滥用权力,腐朽败德,进而提出修德主张,修德的要旨在于“正君心”,这是大本,大本正,才可以正百官、正天下。他寄希望于君心正,去私为公,弃奢为俭,除腐倡廉,慎独好善,近君子而远小人,尚贤使能,虚心纳谏,认为如此方能治理好国家。
至于国家形式的政体,朱熹主张集权与分权并行。宋有鉴于唐的藩镇、五代十国的割据及地方将领权重而尾大不掉的情况,赵匡胤全力使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到了南宋时,由于金朝不断侵扰,地方既无重兵,亦无将领,抗金无力,而有集权与分权之争。朱熹认为,应在集权的原则下,分权于地方,以利地方自保和增强抗金实力。
所谓政治,在朱熹的心目中,是国家的“号令”与刑罚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何保持“天理君权”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为政以德,修德感人。政是为治之具,刑是辅治之法,德礼是所以为治的根本,而德又是礼的根本。另一方面,任贤使能,远嬖近直,君主往往出于一念之间的私心、私欲,而用小人。“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3]这是君主的失职和过错。如果君主周围、政权机构核心之中,都是刚明公正、不谋私利的忠直贤相和贤士,那么,就会主威立,国势强,纲维举,刑政清,民力裕,军政修,人民就能安身立命,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若无经济的发展,富国强兵就不能实现。朱熹认为,民富,君主就不至独贫;民贫,君主也不能独富。他从天理之公、君民一体出发,批评夺民之财而富其君,制止君主对百姓的厚敛,主张省赋恤民,蠲减税钱,除夏秋正税外,其他名目的苛捐杂税统统取消;宁可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
国家要务本节用,所谓务本,民生之本在农,农业生产是社会生存和人类生命延续的先决条件。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民以食为天。因此,他主张不误农时,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保护耕牛,奖励开荒,减免租税,多种经营,增加产量。同时必须节用,裁减军用,削减宗室和官吏俸禄,才能化解赋重民困的局面。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4]民在重税下已无法生活,国家危亡将至。
国家政治、经济受“无形之手”的支配,这无形之手就是其哲学思想,换言之,即其价值观。朱熹被后人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和合儒、道、佛三教,建构了理(太极、道、天理)→气(阴阳)→物(五行、事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它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情形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融突而和合的体系或结合方式,是哲学逻辑内在各层次、要素、部分之间互相冲突、融合而和合的表现形式。
二、认识与统合主客观世界的人本智慧之学
尽管理作为其哲学形上学的核心范畴是无造作、无计度、无情意的,是一个纯然绝对、净洁空阔的世界,但不能真正脱离逻辑结构的关系。
因为理作为“净洁空阔的世界”,必须落实在一个“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是气,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由气使其哲学逻辑结构得以展开聚散、造作、发育流行等活动;由气与理的冲突、融合以及气自身动静变化及理气的“理一分殊”运动,使朱熹哲学逻辑结构具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和辩证思维。
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本体,或称根底。“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5]“本乎一源”的源,即是理,是万物的根底。
理与气、与物既不离,又不杂。从不离说,一方面体认理,必须通过“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使物与理之间保持沟通、会通,消除其间的闭塞;另一方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与物都蕴含着理,人物不离理。从不杂说,“净洁空阔世界”的理,超越人与物。“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6]形上的理是无形无影的,人与物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的。理在逻辑上是先在的、超越的,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
形而上的理,依傍气而化生万物。在化生万物以后,如何由物而体认形而上的理,即由物返归理,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觉、心思、知行等范畴,并以此开展其哲学逻辑结构的体认活动。
朱熹冲决了唐以来“疏不破注”的网罗,敢于改经补经,而作“格物致知补传”。他明言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人心有知,天下的万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是因为知有未尽。“即物穷理”而到极尽处,众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的大用就明白了。格物而获致知的途径是“合内外之理”的过程,即主体人心(内)与客体事物(外)的融合。
格物的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并不是存心于一草一木之间。穷理是涵养本原的功夫,持敬是穷理的根本。“致知”的“致”是推致的意思,即推致我心的知识,以达到全知。格物致知,并不是把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格到,都知会。即使有一二件事不知道,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亦可“识得他破”,“通将去”。类推是由近而远,逐渐理会;由浅入深,层层而进;由粗到精,无所不尽。这样理会多了,便能“自然脱然有悟处”,即对理的觉悟。
持敬是穷理的根本。穷理的要旨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贵于循序而进,达于致精微。致精微的根本在于居敬持志,只有居敬,才能穷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均蕴含着知与行的关系。程颐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认为,程颐是把知与行做“两脚说”。只要把知行分先后,那么,必知先行后。譬如人走路,只有知路如何走,才会走到目的地。知得才能行得,行必依赖于知。若论“知行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即“知轻行重”,注重践行。这是从知的成果上说的。朱熹之所以注重践行,是出于对《尚书》思想的继承。“《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7]行是明理之终,是检验知真不真的标准。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
朱熹既体认到知行互相区别,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又认识到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8]相须,即互相联结、依赖。
格物、即物,物从哪里来?气作为理的“生物之具”,是不可或缺的。“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9]此“散”字是“理一分殊”的分的意思。理一的“一”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本体理,是万殊、阴阳形而上的根据。凡事物都具有对待性的两端,其内与外也具有相对性。“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10]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阴阳,阳中有阴阳;男女各自有阴阳。这就构成对待的普遍性、无限性。
阳为动,阴为静。由于阴阳具有普遍性、无限性,动静便亦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11]即是说他否定运动与静止有端始,而把其看作无限的过程,动静具有相关性、循环性。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动静有端始,是一种割裂动静的思维作怪,是其认知上的局限所致。
朱熹从动静普遍性、无限性出发,提出了运动的化与变两种形态:“化是渐化,变是顿变,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难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固是如此。”[12]渐化是月变、日变、时变,是不被人知觉的、不显著的变化;是渐渐消磨去,如树木渐长,不是突然变化;是无痕迹的变化,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由这些规定可知,其所谓渐化,犹当今所说的量变。渐化在一定限度内,事物仍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内涵和形态;但渐化超出了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变,朱熹称之为顿变。它是一种倏忽、突然的顿变;是显著的、有头面可见的变;顿变是渐化的截断。
朱熹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其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是经学,其诠释的依傍文本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宋代经学超越汉唐,变革古训,进而开出新学风。宋儒以无畏精神解放思想,冲决“五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罗,破除“家法”“师法”的迷信,直接孔孟,以唤回儒学的真精神。朱熹以理体学新思维、以“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诠释经典,重开生命智慧,重建性命道德,重构精神家园。他以“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通经致用,道器一源,理一分殊,体现了宋学经典诠释的真精神。
朱熹以毕生心血注解和研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及“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熹所首创。中国哲学是一开放的体系,每一新学术思潮的诞生,思维形态的转生,核心话题的转换,与其相应地导致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的变换。理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其人文语境是纲常和价值理想的重建;其诠释文本是“四书”,这是理学理论思维形态建构的支柱。
朱熹对《论语》创造性的诠释,表现为无处不以理、天理来解读其义理。如释“仁”为“爱之理”;释“礼”为“天理之节文”;释“朝闻道”的“道”为“事物当然之理”;释“吾道一以贯之”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释“君子喻于义”的“义”为“天理之所宜”;释“性与天道”为“其实一理也”,等等。他把《论语》中的重要概念,都依据自己的理体学思想予以解读,体现了理学的时代精神。虽然这并不一定符合《论语》文本的原意,却赋予《论语》以适应时代的新价值、新生命,变《论语》为朱熹时代的《论语》,使之成为发挥朱熹理体学思想的《论语》,即化旧学为新知。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尊孟思想,对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和郑厚的《艺圃折衷》,逐条予以辨正。他认为孟子乃是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当的人,以批驳以往诽孟的种种言论。认为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孟子辟杨墨,距诐行,放淫辞,使邪说不作,明正道,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强调了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熹自谓“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大学》)”,“某于《大学》用工甚多”。[13]据载,他去世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他之所以注重《大学》,乃是认为其是人之为学的“大坯模”,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概括了修己治人之道,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且从内圣的格致、诚意、正心出发,通过修身,而开出外王的齐、治、平。这是朱熹理体学建构所不可或缺的基石。
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他之所以推崇《中庸》,乃是因为忧道学之失传。程朱继孔孟之道统,揭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遂成为尧、舜、禹、汤至孔、孟的“传授心法”。他将之作为理学“内圣”的要旨,以发明道统。他对《中庸》的分章,是其依理体学理论思维的体认和诠释。
“四书”的编成,使理学学术思潮的理论体系有了依傍经典文本的支撑,使理学思潮的在世发展有了合理性的依据。
朱熹于“四书”用心最多,同时对其他经典亦予以精心的诠释。他是宋易的集大成者,于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经其钻研后,剥去其圣人之言的光环,确定其为卜筮之书的性质。他以理体学为指导,融合义理、图书、象数、卜筮之学。他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二是交易。此两义都以阴阳为着眼点。从阴阳之理说,它是阴阳所以的形上之体;从阴阳之事说,它是形而下之用。
至于“尚书学”,朱熹无专著,然辨伪《古文尚书》为晚出,孔安国的《尚书传》,亦恐是魏晋人所作。他筚路蓝缕,开明清辨伪之端,并指导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
朱熹从20岁开始研究《诗经》,到48岁撰成《诗集传》,他始宗《诗序》,后弃《诗序》,认为《诗序》为后人妄意推想诗人的美刺,不是古人所作,所以不能以《诗序》为证来诠释、理解《诗》的本义。他把诗定义为“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14],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流出。他进而否定了孔子“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教条,认为诗作并非都无邪,而是既然有善,亦有淫邪、淫奔之诗。这是宋代掀起“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表征,标志着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化。
在“礼学”方面,朱熹重礼,早年作《祭礼》《家礼》,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未完成而卒,由其学生续成)。他以《周礼》为纲领,认为“《周礼》规模皆是周公作”,“大纲却是周公意思”。[15]《仪礼》不是古人预先作的,而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再由圣人加以筛选和改进,而编成《仪礼》一书。他认为《礼记》要兼《仪礼》来读,《仪礼》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致使许多礼皆无安著的地方。他从义理层面释《礼记》,以体现理体学的理论思维生命的源泉。
朱熹阐述《春秋》大义,认为体认圣人意蕴,如果在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则是舍本求末;其大义就在于明道正宜,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夷狄。这是《春秋》的大旨,亦是天理所至。他批评一些人以自己的利欲之心诠释《春秋》,揣度圣人之意,属于一种巧说曲解,不符合《春秋》大义本旨。他认为圣人此书之作,是为了遏人欲于横流。遏人欲,是为了存天理。《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史学,《公羊传》《穀梁传》为经学,史学记事详,讲道理差;《公》《穀》于义理上有功,于记事上多误。
朱熹释经,重义理,但并不排斥章句训诂之学。他兼综汉宋,开诠释经典之新风;经传二分,通经求理。“分”以直接体贴经文意蕴;只有不受传统的束缚,才能体认经文本身的义理。“通”以敞开门户,在互相沟通、交感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求索其理。朱熹诠释经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诠释方法、逻辑结构,对经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三、改造人性与行为的身心实践纲领
朱熹形上学的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据,依陈淳的解释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16];性是“在我的理”,是受于天,为我所有。性从生从心,人生来就具是理于吾心,这是从字源上说的。具是理于吾心的性,即是人的本性、本质。
朱熹继承二程“性即理也”,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是理在不同环境、语境下所表现的不同形态,理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心、性、天、命,皆属“一理也”,性与理一样,具有形而上性。“性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17]因而具有度越形器的性质;性是普遍存在的,性无所不有、无处不在,无人无物不具有性,无性便不成其为某人某物。所以说天下没有性外之物;性无形影不可见,这是因为理无形,所以性亦无形。由于性具有寂然至无的性质,因而性是不动的。不动是指性是未发的状态,情是已发状态。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为性,因此有人性与物性,两者既同又异,人与物同具知觉运动之性能,如饥食渴饮等;其异则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是物所不具备的。朱熹继承张载、二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而又超越张、程。他认为,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而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是指理与气杂而言的,并非专指气,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此两性既相互对待,又互相融合。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天命之性,若无气质便无安顿处,犹如水与器皿,水必有盛水的器皿来安顿。同理,若无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就难有所成。
性具于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同道心、人心相联系、相对应。道心是指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的心。“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而无杂,惟一是始终不变,乃能允执厥中。”[18]它与天地之性都是至善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所谓“形气之私”,是指饥求饱、寒求衣之类。若以此为私,圣人也要饥饱寒衣,岂非圣人也为私?于是朱熹做了两方面的修正:一是人心并不是全然不好的,圣人与普通人的分别就在于“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19]普通人以人心为主;二是圣人既具有人心,是否也有人欲?若以人心为人欲,圣人也有人欲之私了。“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人欲也未便是不好”。[20]即他在一定限度内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必要性。
朱熹继承张载“心统性情”说,心之所以能统性情,是因为性情皆出于心,所以心能统御性情。他认为心通贯未发与已发:未发是指人的思虑未接事物,已发是指思虑已与事物接触、相交。无论未发已发,都是一种心的思虑状态,不越于心之外,心贯未发已发的动静。面对心的未发寂然不动的性之静,心的已发感而遂通的情之动,如何体认未发已发?朱熹融合道南学派与湖湘学派,对先涵养后察识与先察识后涵养做了反思,最后回归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论思维上来,在心统性情、心有体用、性情未发已发体认中,建构了以心贯未发已发、体用、性情的逻辑结构,标志着其既度越道南一派,又意在度越程颐的和合纵贯与横摄系统的气魄。
朱熹从理体学的天命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心性论出发,探讨了天理与人欲问题,为重建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总结古今诸家理欲之争的得失,阐发了“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认为天理就是纲常,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天理既是“五常”,未有不善的。当心处于未有思虑之萌的未发时,心中浑是天理,无一丝人欲之杂,这是心的本然。人欲之私之所以有,是因为人生来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浊偏正的不同,物欲有浅深厚薄的差别,是生而具有的;人有耳目鼻口的欲望,而不能克己,终于丧失了天理,这是被私欲所蔽的结果。
天理与人欲既对待又融合。从对待而言,蕴含着公私、是非的分野,即天理之公、之是,人欲之私、之非。其关系形态是一方战胜一方、一方克服一方和互相消长:天理少则人欲多,人欲少则天理多,最终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21]。从融合的维度而言,“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22]。人欲是从天理里面做出来的。两者相互依存,共处一个和合体中。因此“人欲中自有天理”[23]。两者互相包容,界限难分。
天理人欲之辩与义利之辩相关。朱熹以义为天理之所宜,乃是指“合当”,即应当、当做之意。天理所当做的,便合乎义;义是心之制,事之宜,以义理之心的价值裁制万事,乃是人心所固有的仁义之心。利是人情之所欲,小人只计较对自己有利或无利,而不顾义理价值;利是人欲之私,即指满足自己人欲的自私自利。
朱熹分利为公利与私利,为天下正大的道理去谋利,即为天下国家、社会谋利,这是公利,此利即是义。如作为地方官吏,实行奖励生产、开荒救灾、薄赋轻徭等措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种重利就是为公谋利,而不是为私利。但作为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言,应重义轻利,绝不为私谋利。事无大小,都要分清义利、善恶、是非,这关系着政治清浊、好坏,国家兴衰、存亡。
朱熹倾力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并将此贯彻到教育的实践之中。他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每到一地,整顿县学、州学;他创办同安县学、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书堂等,恢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制定学规,编撰教材,培养了一大批学者。
朱熹教育的宗旨、目标、内涵,体现在其《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规定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人之要。”[24]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五伦”,这是圣人教人的“定本”。他以此复求圣人之意,以明性命道德之归,重建伦理道德的需要,以纠正忘本逐末、怀利去义之学;从修身、处事、接人之要的教育中,提升道德情操,以改变风俗日敝、人才日衰的情况;以存天理、灭人欲,诚意正心,培养圣人之德。
朱熹把教育按照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8岁入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以培养具有基本道德文化素质的青少年;大学为15岁以后,教以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朱熹思想从南宋末至元,其理论思维价值逐渐为人所认知。元朝科举取士,钦定《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它传播到朝鲜半岛及日本、越南等国,亦渐次成为其官方哲学。在朝鲜,从高丽末的安珦(1243—1306)随忠烈王赴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回国后在国子监教授程朱道学始,到李朝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其间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朱子学大家,并分为主理派、主气派、折中派和求实派等,[25]可谓群星灿烂。在日本,朱子学传入较早,1211年日本僧侣俊芿回国时带回《四书章句集注》初刻本,在“五山十刹”时期,实施了以僧侣为主体的汉文学讲授,同时研讨朱子学,促使日本朱子学影响的扩大,后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朱子学家。1603年以后,它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就其师承关系而言,可分为京师、海西、海南、大阪、宽政、水户等朱子学派。越南也曾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26]
朱子学在其与传播所在国的传统文化的融合中,逐步发展为朝鲜朱子学、日本朱子学、越南朱子学,并各具特色,五彩纷呈。可以说,朱熹的思想不但是古代中国化育人心及调理社会的思想体系之一,而且业已对现当代中国人乃至亚洲各国大众之道德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体现了古今相通、人心相合的生命常青力及永久价值。
中华文化注重笃行,主张知行合一。任何思想与理论如果不能转化为行动,则不啻为空谈。尤其是对于古代哲学乃至人文思想而言,我们现今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的当务之急,乃是对之进行与时偕行、囊括古今中外成果和全人类智慧的思想内容集成、批判性扬弃、时代价值阐发、社会人文意义掘析、应用路径探究和实践性体用转化;如此方能真正使之通过不断推陈出新和与时偕行而得以实现其人本性的价值转化:代代生根发芽、辈辈开花结果,借此方能永葆国学精神和民族思想智慧之永久生机。从广义和终极角度而言,人心之用和人体之用,乃是一切人文思想及理论的根本目标所在、根本价值的体现和生命活力的无尽源泉所在。
一、造益古代政治经济的理性观念
洞悉天理,这是朱熹思想哲学的核心话题,是其政治、经济、哲学、经学、美学、道德、教育等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理(天理)在朱熹的思想逻辑体系中,是形而上本体。“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1]理是亘古亘今,常存不灭,超越人物生灭的无限,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根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2]。天地人及其性,都以理为所以然者,以理为终极的根源。
由此,政治为天理政治,变以往“君权神授”为“天理君权”,革“天授君权”为“理授君权”,但他不完全否定天威,仍以天威来劝诫、约束君威、君权,使之不过分膨胀,滥用权力,腐朽败德,进而提出修德主张,修德的要旨在于“正君心”,这是大本,大本正,才可以正百官、正天下。他寄希望于君心正,去私为公,弃奢为俭,除腐倡廉,慎独好善,近君子而远小人,尚贤使能,虚心纳谏,认为如此方能治理好国家。
至于国家形式的政体,朱熹主张集权与分权并行。宋有鉴于唐的藩镇、五代十国的割据及地方将领权重而尾大不掉的情况,赵匡胤全力使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到了南宋时,由于金朝不断侵扰,地方既无重兵,亦无将领,抗金无力,而有集权与分权之争。朱熹认为,应在集权的原则下,分权于地方,以利地方自保和增强抗金实力。
所谓政治,在朱熹的心目中,是国家的“号令”与刑罚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何保持“天理君权”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为政以德,修德感人。政是为治之具,刑是辅治之法,德礼是所以为治的根本,而德又是礼的根本。另一方面,任贤使能,远嬖近直,君主往往出于一念之间的私心、私欲,而用小人。“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3]这是君主的失职和过错。如果君主周围、政权机构核心之中,都是刚明公正、不谋私利的忠直贤相和贤士,那么,就会主威立,国势强,纲维举,刑政清,民力裕,军政修,人民就能安身立命,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若无经济的发展,富国强兵就不能实现。朱熹认为,民富,君主就不至独贫;民贫,君主也不能独富。他从天理之公、君民一体出发,批评夺民之财而富其君,制止君主对百姓的厚敛,主张省赋恤民,蠲减税钱,除夏秋正税外,其他名目的苛捐杂税统统取消;宁可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
国家要务本节用,所谓务本,民生之本在农,农业生产是社会生存和人类生命延续的先决条件。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民以食为天。因此,他主张不误农时,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保护耕牛,奖励开荒,减免租税,多种经营,增加产量。同时必须节用,裁减军用,削减宗室和官吏俸禄,才能化解赋重民困的局面。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4]民在重税下已无法生活,国家危亡将至。
国家政治、经济受“无形之手”的支配,这无形之手就是其哲学思想,换言之,即其价值观。朱熹被后人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和合儒、道、佛三教,建构了理(太极、道、天理)→气(阴阳)→物(五行、事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它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情形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融突而和合的体系或结合方式,是哲学逻辑内在各层次、要素、部分之间互相冲突、融合而和合的表现形式。
二、认识与统合主客观世界的人本智慧之学
尽管理作为其哲学形上学的核心范畴是无造作、无计度、无情意的,是一个纯然绝对、净洁空阔的世界,但不能真正脱离逻辑结构的关系。
因为理作为“净洁空阔的世界”,必须落实在一个“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是气,气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由气使其哲学逻辑结构得以展开聚散、造作、发育流行等活动;由气与理的冲突、融合以及气自身动静变化及理气的“理一分殊”运动,使朱熹哲学逻辑结构具有生气勃勃的生命力和辩证思维。
理(太极、道、天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本体,或称根底。“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5]“本乎一源”的源,即是理,是万物的根底。
理与气、与物既不离,又不杂。从不离说,一方面体认理,必须通过“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使物与理之间保持沟通、会通,消除其间的闭塞;另一方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与物都蕴含着理,人物不离理。从不杂说,“净洁空阔世界”的理,超越人与物。“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6]形上的理是无形无影的,人与物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的。理在逻辑上是先在的、超越的,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
形而上的理,依傍气而化生万物。在化生万物以后,如何由物而体认形而上的理,即由物返归理,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觉、心思、知行等范畴,并以此开展其哲学逻辑结构的体认活动。
朱熹冲决了唐以来“疏不破注”的网罗,敢于改经补经,而作“格物致知补传”。他明言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人心有知,天下的万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是因为知有未尽。“即物穷理”而到极尽处,众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的大用就明白了。格物而获致知的途径是“合内外之理”的过程,即主体人心(内)与客体事物(外)的融合。
格物的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并不是存心于一草一木之间。穷理是涵养本原的功夫,持敬是穷理的根本。“致知”的“致”是推致的意思,即推致我心的知识,以达到全知。格物致知,并不是把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格到,都知会。即使有一二件事不知道,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亦可“识得他破”,“通将去”。类推是由近而远,逐渐理会;由浅入深,层层而进;由粗到精,无所不尽。这样理会多了,便能“自然脱然有悟处”,即对理的觉悟。
持敬是穷理的根本。穷理的要旨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贵于循序而进,达于致精微。致精微的根本在于居敬持志,只有居敬,才能穷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均蕴含着知与行的关系。程颐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认为,程颐是把知与行做“两脚说”。只要把知行分先后,那么,必知先行后。譬如人走路,只有知路如何走,才会走到目的地。知得才能行得,行必依赖于知。若论“知行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即“知轻行重”,注重践行。这是从知的成果上说的。朱熹之所以注重践行,是出于对《尚书》思想的继承。“《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7]行是明理之终,是检验知真不真的标准。必待行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
朱熹既体认到知行互相区别,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又认识到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8]相须,即互相联结、依赖。
格物、即物,物从哪里来?气作为理的“生物之具”,是不可或缺的。“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9]此“散”字是“理一分殊”的分的意思。理一的“一”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形上本体理,是万殊、阴阳形而上的根据。凡事物都具有对待性的两端,其内与外也具有相对性。“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10]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阴阳,阳中有阴阳;男女各自有阴阳。这就构成对待的普遍性、无限性。
阳为动,阴为静。由于阴阳具有普遍性、无限性,动静便亦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朱熹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今以太极观之,虽曰‘动而生阳’,毕竟未动之前须静,静之前又须是动。推而上之,何自见其端与始。”[11]即是说他否定运动与静止有端始,而把其看作无限的过程,动静具有相关性、循环性。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动静有端始,是一种割裂动静的思维作怪,是其认知上的局限所致。
朱熹从动静普遍性、无限性出发,提出了运动的化与变两种形态:“化是渐化,变是顿变,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难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固是如此。”[12]渐化是月变、日变、时变,是不被人知觉的、不显著的变化;是渐渐消磨去,如树木渐长,不是突然变化;是无痕迹的变化,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由这些规定可知,其所谓渐化,犹当今所说的量变。渐化在一定限度内,事物仍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内涵和形态;但渐化超出了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变,朱熹称之为顿变。它是一种倏忽、突然的顿变;是显著的、有头面可见的变;顿变是渐化的截断。
朱熹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其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是经学,其诠释的依傍文本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宋代经学超越汉唐,变革古训,进而开出新学风。宋儒以无畏精神解放思想,冲决“五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网罗,破除“家法”“师法”的迷信,直接孔孟,以唤回儒学的真精神。朱熹以理体学新思维、以“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诠释经典,重开生命智慧,重建性命道德,重构精神家园。他以“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通经致用,道器一源,理一分殊,体现了宋学经典诠释的真精神。
朱熹以毕生心血注解和研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及“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熹所首创。中国哲学是一开放的体系,每一新学术思潮的诞生,思维形态的转生,核心话题的转换,与其相应地导致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的变换。理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理、气、心、性;其人文语境是纲常和价值理想的重建;其诠释文本是“四书”,这是理学理论思维形态建构的支柱。
朱熹对《论语》创造性的诠释,表现为无处不以理、天理来解读其义理。如释“仁”为“爱之理”;释“礼”为“天理之节文”;释“朝闻道”的“道”为“事物当然之理”;释“吾道一以贯之”为“圣人之心,浑然一理”;释“君子喻于义”的“义”为“天理之所宜”;释“性与天道”为“其实一理也”,等等。他把《论语》中的重要概念,都依据自己的理体学思想予以解读,体现了理学的时代精神。虽然这并不一定符合《论语》文本的原意,却赋予《论语》以适应时代的新价值、新生命,变《论语》为朱熹时代的《论语》,使之成为发挥朱熹理体学思想的《论语》,即化旧学为新知。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尊孟思想,对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和郑厚的《艺圃折衷》,逐条予以辨正。他认为孟子乃是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当的人,以批驳以往诽孟的种种言论。认为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孟子辟杨墨,距诐行,放淫辞,使邪说不作,明正道,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强调了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熹自谓“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大学》)”,“某于《大学》用工甚多”。[13]据载,他去世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他之所以注重《大学》,乃是认为其是人之为学的“大坯模”,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概括了修己治人之道,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且从内圣的格致、诚意、正心出发,通过修身,而开出外王的齐、治、平。这是朱熹理体学建构所不可或缺的基石。
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他之所以推崇《中庸》,乃是因为忧道学之失传。程朱继孔孟之道统,揭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遂成为尧、舜、禹、汤至孔、孟的“传授心法”。他将之作为理学“内圣”的要旨,以发明道统。他对《中庸》的分章,是其依理体学理论思维的体认和诠释。
“四书”的编成,使理学学术思潮的理论体系有了依傍经典文本的支撑,使理学思潮的在世发展有了合理性的依据。
朱熹于“四书”用心最多,同时对其他经典亦予以精心的诠释。他是宋易的集大成者,于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经其钻研后,剥去其圣人之言的光环,确定其为卜筮之书的性质。他以理体学为指导,融合义理、图书、象数、卜筮之学。他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二是交易。此两义都以阴阳为着眼点。从阴阳之理说,它是阴阳所以的形上之体;从阴阳之事说,它是形而下之用。
至于“尚书学”,朱熹无专著,然辨伪《古文尚书》为晚出,孔安国的《尚书传》,亦恐是魏晋人所作。他筚路蓝缕,开明清辨伪之端,并指导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
朱熹从20岁开始研究《诗经》,到48岁撰成《诗集传》,他始宗《诗序》,后弃《诗序》,认为《诗序》为后人妄意推想诗人的美刺,不是古人所作,所以不能以《诗序》为证来诠释、理解《诗》的本义。他把诗定义为“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14],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流出。他进而否定了孔子“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教条,认为诗作并非都无邪,而是既然有善,亦有淫邪、淫奔之诗。这是宋代掀起“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表征,标志着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化。
在“礼学”方面,朱熹重礼,早年作《祭礼》《家礼》,晚年撰《仪礼经传通解》(未完成而卒,由其学生续成)。他以《周礼》为纲领,认为“《周礼》规模皆是周公作”,“大纲却是周公意思”。[15]《仪礼》不是古人预先作的,而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再由圣人加以筛选和改进,而编成《仪礼》一书。他认为《礼记》要兼《仪礼》来读,《仪礼》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致使许多礼皆无安著的地方。他从义理层面释《礼记》,以体现理体学的理论思维生命的源泉。
朱熹阐述《春秋》大义,认为体认圣人意蕴,如果在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则是舍本求末;其大义就在于明道正宜,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夷狄。这是《春秋》的大旨,亦是天理所至。他批评一些人以自己的利欲之心诠释《春秋》,揣度圣人之意,属于一种巧说曲解,不符合《春秋》大义本旨。他认为圣人此书之作,是为了遏人欲于横流。遏人欲,是为了存天理。《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史学,《公羊传》《穀梁传》为经学,史学记事详,讲道理差;《公》《穀》于义理上有功,于记事上多误。
朱熹释经,重义理,但并不排斥章句训诂之学。他兼综汉宋,开诠释经典之新风;经传二分,通经求理。“分”以直接体贴经文意蕴;只有不受传统的束缚,才能体认经文本身的义理。“通”以敞开门户,在互相沟通、交感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求索其理。朱熹诠释经学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诠释方法、逻辑结构,对经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三、改造人性与行为的身心实践纲领
朱熹形上学的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据,依陈淳的解释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16];性是“在我的理”,是受于天,为我所有。性从生从心,人生来就具是理于吾心,这是从字源上说的。具是理于吾心的性,即是人的本性、本质。
朱熹继承二程“性即理也”,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是理在不同环境、语境下所表现的不同形态,理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心、性、天、命,皆属“一理也”,性与理一样,具有形而上性。“性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17]因而具有度越形器的性质;性是普遍存在的,性无所不有、无处不在,无人无物不具有性,无性便不成其为某人某物。所以说天下没有性外之物;性无形影不可见,这是因为理无形,所以性亦无形。由于性具有寂然至无的性质,因而性是不动的。不动是指性是未发的状态,情是已发状态。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为性,因此有人性与物性,两者既同又异,人与物同具知觉运动之性能,如饥食渴饮等;其异则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是物所不具备的。朱熹继承张载、二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而又超越张、程。他认为,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而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是指理与气杂而言的,并非专指气,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此两性既相互对待,又互相融合。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本然之性。天命之性,若无气质便无安顿处,犹如水与器皿,水必有盛水的器皿来安顿。同理,若无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就难有所成。
性具于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同道心、人心相联系、相对应。道心是指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的心。“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而无杂,惟一是始终不变,乃能允执厥中。”[18]它与天地之性都是至善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所谓“形气之私”,是指饥求饱、寒求衣之类。若以此为私,圣人也要饥饱寒衣,岂非圣人也为私?于是朱熹做了两方面的修正:一是人心并不是全然不好的,圣人与普通人的分别就在于“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19]普通人以人心为主;二是圣人既具有人心,是否也有人欲?若以人心为人欲,圣人也有人欲之私了。“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人欲也未便是不好”。[20]即他在一定限度内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必要性。
朱熹继承张载“心统性情”说,心之所以能统性情,是因为性情皆出于心,所以心能统御性情。他认为心通贯未发与已发:未发是指人的思虑未接事物,已发是指思虑已与事物接触、相交。无论未发已发,都是一种心的思虑状态,不越于心之外,心贯未发已发的动静。面对心的未发寂然不动的性之静,心的已发感而遂通的情之动,如何体认未发已发?朱熹融合道南学派与湖湘学派,对先涵养后察识与先察识后涵养做了反思,最后回归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论思维上来,在心统性情、心有体用、性情未发已发体认中,建构了以心贯未发已发、体用、性情的逻辑结构,标志着其既度越道南一派,又意在度越程颐的和合纵贯与横摄系统的气魄。
朱熹从理体学的天命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心性论出发,探讨了天理与人欲问题,为重建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总结古今诸家理欲之争的得失,阐发了“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他认为天理就是纲常,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天理既是“五常”,未有不善的。当心处于未有思虑之萌的未发时,心中浑是天理,无一丝人欲之杂,这是心的本然。人欲之私之所以有,是因为人生来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浊偏正的不同,物欲有浅深厚薄的差别,是生而具有的;人有耳目鼻口的欲望,而不能克己,终于丧失了天理,这是被私欲所蔽的结果。
天理与人欲既对待又融合。从对待而言,蕴含着公私、是非的分野,即天理之公、之是,人欲之私、之非。其关系形态是一方战胜一方、一方克服一方和互相消长:天理少则人欲多,人欲少则天理多,最终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21]。从融合的维度而言,“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22]。人欲是从天理里面做出来的。两者相互依存,共处一个和合体中。因此“人欲中自有天理”[23]。两者互相包容,界限难分。
天理人欲之辩与义利之辩相关。朱熹以义为天理之所宜,乃是指“合当”,即应当、当做之意。天理所当做的,便合乎义;义是心之制,事之宜,以义理之心的价值裁制万事,乃是人心所固有的仁义之心。利是人情之所欲,小人只计较对自己有利或无利,而不顾义理价值;利是人欲之私,即指满足自己人欲的自私自利。
朱熹分利为公利与私利,为天下正大的道理去谋利,即为天下国家、社会谋利,这是公利,此利即是义。如作为地方官吏,实行奖励生产、开荒救灾、薄赋轻徭等措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种重利就是为公谋利,而不是为私利。但作为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言,应重义轻利,绝不为私谋利。事无大小,都要分清义利、善恶、是非,这关系着政治清浊、好坏,国家兴衰、存亡。
朱熹倾力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并将此贯彻到教育的实践之中。他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每到一地,整顿县学、州学;他创办同安县学、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书堂等,恢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制定学规,编撰教材,培养了一大批学者。
朱熹教育的宗旨、目标、内涵,体现在其《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规定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人之要。”[24]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五伦”,这是圣人教人的“定本”。他以此复求圣人之意,以明性命道德之归,重建伦理道德的需要,以纠正忘本逐末、怀利去义之学;从修身、处事、接人之要的教育中,提升道德情操,以改变风俗日敝、人才日衰的情况;以存天理、灭人欲,诚意正心,培养圣人之德。
朱熹把教育按照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8岁入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以培养具有基本道德文化素质的青少年;大学为15岁以后,教以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朱熹思想从南宋末至元,其理论思维价值逐渐为人所认知。元朝科举取士,钦定《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它传播到朝鲜半岛及日本、越南等国,亦渐次成为其官方哲学。在朝鲜,从高丽末的安珦(1243—1306)随忠烈王赴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回国后在国子监教授程朱道学始,到李朝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其间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朱子学大家,并分为主理派、主气派、折中派和求实派等,[25]可谓群星灿烂。在日本,朱子学传入较早,1211年日本僧侣俊芿回国时带回《四书章句集注》初刻本,在“五山十刹”时期,实施了以僧侣为主体的汉文学讲授,同时研讨朱子学,促使日本朱子学影响的扩大,后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朱子学家。1603年以后,它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就其师承关系而言,可分为京师、海西、海南、大阪、宽政、水户等朱子学派。越南也曾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26]
朱子学在其与传播所在国的传统文化的融合中,逐步发展为朝鲜朱子学、日本朱子学、越南朱子学,并各具特色,五彩纷呈。可以说,朱熹的思想不但是古代中国化育人心及调理社会的思想体系之一,而且业已对现当代中国人乃至亚洲各国大众之道德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体现了古今相通、人心相合的生命常青力及永久价值。
附注
注释:
[1]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读大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3]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己酉拟上封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4]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08页。
[5]朱熹:《朱子遗书·延平答问》,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
[6]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答江德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7]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3页。
[8]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页。
[9]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页。
[10]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74页。
[11]同上书,第2376页。
[12]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85页。
[13]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8页。
[14]朱熹:《诗集传·序》,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15]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03页。
[16]陈淳:《北溪先生字义详讲》卷下,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
[17]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7页。
[18]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13页。
[19]同上书,第2009页。
[20]同上书,第2010页。
[21]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5页。
[22]同上书,第223页。
[23]同上书,第224页。
[24]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5]张立文:《李退溪思想世界·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6]张立文:《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序二》,北京:华夏出版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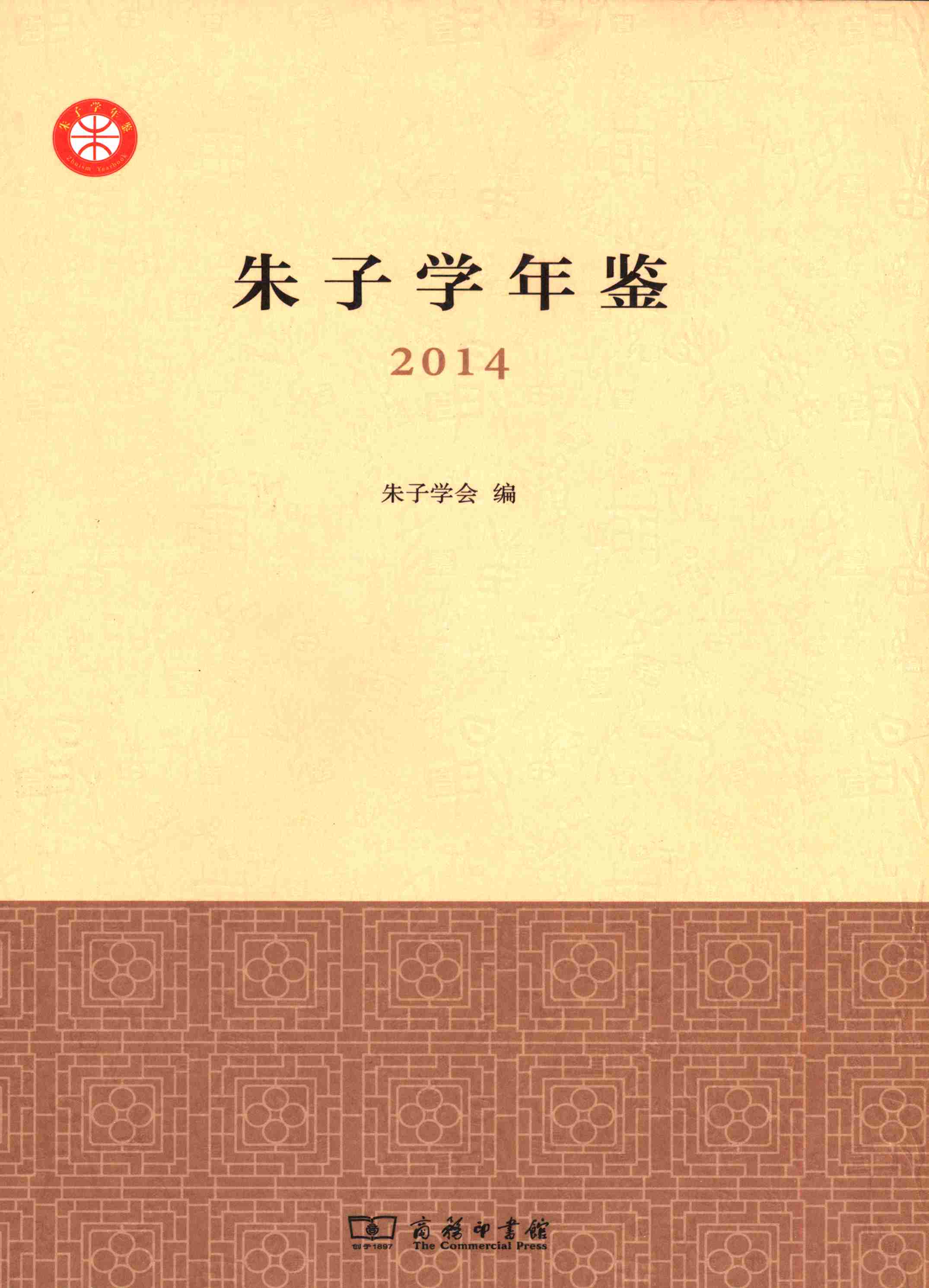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4》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分为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等九个栏目,收录了《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张立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