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熹心性之学的原初探索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4》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669 |
| 颗粒名称: | 一、朱熹心性之学的原初探索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 |
| 页码: | 008-01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在与张栻的讨论中,对于《中庸》中情之未发和中节之和的理解存在困惑。他怀疑自己如何从自身的体验中把握和体验到情之未发的中。程颐在《近思录》中回应苏炳的提问,认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追求其中的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追求本身就已经涉及到思虑和发展,不再是未发状态。 |
| 关键词: | 朱熹 张栻 心性之学 |
内容
1167年,37岁的朱熹从福建崇安赴湖南长沙,往见张栻以论学,两人对于心性之学多有探讨。其岁前后,朱子正处在整理《二程遗书》之际。先前,他始受学于三先生,继而受李延平的影响,进入了理学思考的殿堂。但当时的朱熹仍于一事处存惑待解:到底怎么从自己的体验中来掌握、来体验《中庸》所说的情之已发、未发问题?从《中庸》处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后者是可体验的,前者则不能被体验、不涉于“和”的境界。从认识体验的角度来说,“中”处存有一个大问题,因为“中”是未发之“中”,既然是未发,就无法体察“中”是何物。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讲,发而不中节,便不能体验到中节之和,如此则怎么去修养?这便是朱子存疑之所在,也涉及程颐在《近思录》中对苏炳所提的未发如何体察之问题的回应。
在《近思录》的《存养》篇中,苏季明(炳)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程颐答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2]程颐认为,既思于未发之前求之,就不可能“求”到其“中”。因为所谓“求”者,已然是一种思虑了;假若要在得“中”于未发之前,就不能去“求”之、去掌握它——否则即是已发,而只能去感受它、去“存养”它。他说:“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苏季明所问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这当然是不可以的;若要称“求”,便不能说是未发。这便是此中的第一个命题。
其后,程颐提出了第二个命题:人无法在喜怒哀乐之前去“求”乎其“中”,故若要把握“中”,就必须“涵养”“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3]知觉即已是动,故程颐在这段话里提到喜怒哀乐已发之时,乃谓需要存养,亦只能说存养。所谓存养者,即能够感受到(不能说思虑到)未发之“中”,指对“中”的逐渐之体验和保存。而“存养”“涵养”者,自需要长期之修持。他又说,凭着“涵养”,虽无所见、无所闻,但能有夫知觉。“涵养”之中包含了一种知觉;这种知觉,不但可使长时间之“涵养”拥有感知、体验的能力,而且使喜怒哀乐均能发而中节。推进一步而言,“涵养”不能只谓是一种静。程颐反对佛家之静,谓“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认为若能知觉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见天地之心”,就已是一种动了,不复能说是静。对于心的活动而言,与其言动静,不如谓“心”之“动”中更有个“敬”。程颐亦有这方面的了悟,认为先秦儒家圣人有一种“止”与“敬”的观点,类乎释氏之谓“定”者,即指在“动”之中找到内含的性体,即潜在的“中”之状态。“中”含有人性之本、之正的意思,这样的“中”,才能在没有私欲的情况之下,发展为“和”。程颐谓,在知的体验中能看到知觉,看到天理之所在。静中不是无物,是有物——即“敬”。若要去掌握这样一个能体会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性”之本体状态,就要求“性”做到“定”,在动中有所止。程颐把它界定为“莫若主一”,意思是须有个主宰,在敬中乃不会流入寂静——即不会倒向佛学的命题;而又不至于分散,所以谓之“主一”。故而,程颐对苏炳开示,谓只有主敬才能认识“中”。这就是“敬中涵养”的命题。
苏炳又自陈“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程颐认为,这就是“不诚之本”。[4]“诚”的工夫即:当我在动中知觉之时,能有所止,并能够对这个所止有所贞定,这就是“诚”——即能够坚持之意。兹“诚”是一种真实的状态,要掌握诚就要做到专一,这里便显示了心的作用。
这段涉及心性之学的论述,在二程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含义、启示。我将此视为本文面对的基本问题,把程颐对此的解说当作重点加以分析。借以说明何以后来朱熹在编订《二程遗书》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决心要对此问题做出解答,因而产生了对《中庸》所述中和概念的先后认识;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此举是有其必然性的。
此外,朱熹两见李延平,其中一次见面之际,李延平指导朱熹要在平日里注意静坐。朱熹一开始并没能领会:静坐并非要归于寂静,而是要在心的知觉活动中体会、把握并坚持人性之“中”及心能为善的状态及潜力;经过这一工夫问题,然后才能够用之于事、用之于行而不偏离,不受人欲的影响,进而能够达到一种终极之“和”,即能应对处事行为上能恰到好处、能产生转化为合理性的作用、能合乎意而发于情、能表达仁而合乎义。这是人性之中的一种重要感知。
以上的论述之所以重要,是因其说明了朱子为何要与张南轩见面,以论心性修持问题的背景。朱子要了解心与性的关系。心可以体会、知觉、存养,而性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原始状态。如何掌握这种状态,使之能发挥“和”,而非偏向一种不正不和,这自是相当重要的。但试图掌握此一原始状态、掌握性之“中”时,并不一定会得到“和”,这涉及修养的工夫问题。不过,掌握到性之“中”,至少就能更好地发挥情之“和”,更好地践行合情合理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朱子当初面对此一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解决。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为了对朱子访问张栻有基本的说明,也能了解朱子在论学中如何受到张南轩的影响,而得到性体心用(“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5])的结论;当然,他回到福建后对此观点又有所不满,显然反映了他对程子答苏季明所问喜怒哀乐未发是性而非心的问题仍有保留。他不能单纯地把性体心用之说当作最后结论,而必须要考虑一个新的更为完整的典范。
首先,朱子将性情心之关系,看作是心之统合性情,即“心统性情”[6],是由于心能存养于未发之“中”。心能照顾性、能参与情,故有心统性情的表达。事实上,张载已在早前提过心统性情的观点,南轩则提出了“心主性情”[7]的看法。朱子后来固然没有同意心主性情之论,但其定于心统性情的观点也不能排除心主性情的含义。朱子经过与张南轩的论辩,他亦必须承认心主性情也合乎程子的原意。“心”能统合与包含,但也有主宰与影响的含义在其中。对朱子来说,这样一个理解之过程,正是他从所谓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过程。
要说明此一过程中的转变,我们还需要补充两个学术背景,一个是张载之学,一个是胡宏之学。张载写《正蒙》,强调气化之性的重要性。他在《太和》篇中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8],这段话很重要。所谓人之性者,其所成由天道而来,天道又是由太虚通过气化而产生的一种运行,这种运行又与具有本体性的“虚”,即太虚之气相合,亦即由天道之动产生万物的品类流行,可谓为生生之性。对于人而言,“性”有了本体性也是个体性的潜能,以万物为机缘,才有一种知觉,才产生了“心”。
以张载作为论性的开始,才能更好地说明二程对天理的突出认识。大程认为,事物之所以成其然,莫非天理,对天理的体验是心对品类万物与天道流行的最大感受。天理可说包含在天道之中,使万物终于成为宇宙中的品类,而心作为觉知与感应之体,才能觉知而体验天道的万物,产生天理的概念。所谓天理者乃事物自然而必然的存在状态。当然,二程并没有就这个宇宙的本体处说起,而是就人的心性的体验来理会,即“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9],兹亦合乎所谓“天命之谓性”者。“性”就是天之所命,亦可谓是道之化成。有了这个背景之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二程所谓的性,中间已经有理的成分,也有气的成分,亦有天道的成分。所以“性”是事物存在的枢纽。后来胡五峰对此有所发挥,乃谓事物必须就“性”而谈,舍之则无法论物。此中包含了一种传承:张载影响二程,二程影响胡五峰。再者,上文谓小程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个“中”实际上就是“性”,而此“性”也可以说为张载所说合乎理之气化本体原始和谐状态。朱子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所可知的是:胡五峰是杨时的弟子,杨时又是二程的弟子,从杨时到胡五峰之思虑传承重点均放在对性的体悟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虽然《论语》中所谓性与天道是夫子所不多谈的,但夫子并非完全没有相应的观点。要解决性与天道的问题,就必须在此致力。这种探讨要经过一种体悟、体察、体会,再把它变成一种察识,实际上是体悟人性之“中”,然后发挥人性之“和”的实践之工夫。[10]朱子欲论性之本体,就必须要对“‘心’如何主导‘体’”的问题具备一种重新的认识。故他乃不得不面向湖湘学派进行探讨。
在《近思录》的《存养》篇中,苏季明(炳)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程颐答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2]程颐认为,既思于未发之前求之,就不可能“求”到其“中”。因为所谓“求”者,已然是一种思虑了;假若要在得“中”于未发之前,就不能去“求”之、去掌握它——否则即是已发,而只能去感受它、去“存养”它。他说:“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苏季明所问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这当然是不可以的;若要称“求”,便不能说是未发。这便是此中的第一个命题。
其后,程颐提出了第二个命题:人无法在喜怒哀乐之前去“求”乎其“中”,故若要把握“中”,就必须“涵养”“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3]知觉即已是动,故程颐在这段话里提到喜怒哀乐已发之时,乃谓需要存养,亦只能说存养。所谓存养者,即能够感受到(不能说思虑到)未发之“中”,指对“中”的逐渐之体验和保存。而“存养”“涵养”者,自需要长期之修持。他又说,凭着“涵养”,虽无所见、无所闻,但能有夫知觉。“涵养”之中包含了一种知觉;这种知觉,不但可使长时间之“涵养”拥有感知、体验的能力,而且使喜怒哀乐均能发而中节。推进一步而言,“涵养”不能只谓是一种静。程颐反对佛家之静,谓“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认为若能知觉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见天地之心”,就已是一种动了,不复能说是静。对于心的活动而言,与其言动静,不如谓“心”之“动”中更有个“敬”。程颐亦有这方面的了悟,认为先秦儒家圣人有一种“止”与“敬”的观点,类乎释氏之谓“定”者,即指在“动”之中找到内含的性体,即潜在的“中”之状态。“中”含有人性之本、之正的意思,这样的“中”,才能在没有私欲的情况之下,发展为“和”。程颐谓,在知的体验中能看到知觉,看到天理之所在。静中不是无物,是有物——即“敬”。若要去掌握这样一个能体会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性”之本体状态,就要求“性”做到“定”,在动中有所止。程颐把它界定为“莫若主一”,意思是须有个主宰,在敬中乃不会流入寂静——即不会倒向佛学的命题;而又不至于分散,所以谓之“主一”。故而,程颐对苏炳开示,谓只有主敬才能认识“中”。这就是“敬中涵养”的命题。
苏炳又自陈“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程颐认为,这就是“不诚之本”。[4]“诚”的工夫即:当我在动中知觉之时,能有所止,并能够对这个所止有所贞定,这就是“诚”——即能够坚持之意。兹“诚”是一种真实的状态,要掌握诚就要做到专一,这里便显示了心的作用。
这段涉及心性之学的论述,在二程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含义、启示。我将此视为本文面对的基本问题,把程颐对此的解说当作重点加以分析。借以说明何以后来朱熹在编订《二程遗书》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决心要对此问题做出解答,因而产生了对《中庸》所述中和概念的先后认识;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此举是有其必然性的。
此外,朱熹两见李延平,其中一次见面之际,李延平指导朱熹要在平日里注意静坐。朱熹一开始并没能领会:静坐并非要归于寂静,而是要在心的知觉活动中体会、把握并坚持人性之“中”及心能为善的状态及潜力;经过这一工夫问题,然后才能够用之于事、用之于行而不偏离,不受人欲的影响,进而能够达到一种终极之“和”,即能应对处事行为上能恰到好处、能产生转化为合理性的作用、能合乎意而发于情、能表达仁而合乎义。这是人性之中的一种重要感知。
以上的论述之所以重要,是因其说明了朱子为何要与张南轩见面,以论心性修持问题的背景。朱子要了解心与性的关系。心可以体会、知觉、存养,而性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原始状态。如何掌握这种状态,使之能发挥“和”,而非偏向一种不正不和,这自是相当重要的。但试图掌握此一原始状态、掌握性之“中”时,并不一定会得到“和”,这涉及修养的工夫问题。不过,掌握到性之“中”,至少就能更好地发挥情之“和”,更好地践行合情合理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朱子当初面对此一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解决。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为了对朱子访问张栻有基本的说明,也能了解朱子在论学中如何受到张南轩的影响,而得到性体心用(“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5])的结论;当然,他回到福建后对此观点又有所不满,显然反映了他对程子答苏季明所问喜怒哀乐未发是性而非心的问题仍有保留。他不能单纯地把性体心用之说当作最后结论,而必须要考虑一个新的更为完整的典范。
首先,朱子将性情心之关系,看作是心之统合性情,即“心统性情”[6],是由于心能存养于未发之“中”。心能照顾性、能参与情,故有心统性情的表达。事实上,张载已在早前提过心统性情的观点,南轩则提出了“心主性情”[7]的看法。朱子后来固然没有同意心主性情之论,但其定于心统性情的观点也不能排除心主性情的含义。朱子经过与张南轩的论辩,他亦必须承认心主性情也合乎程子的原意。“心”能统合与包含,但也有主宰与影响的含义在其中。对朱子来说,这样一个理解之过程,正是他从所谓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过程。
要说明此一过程中的转变,我们还需要补充两个学术背景,一个是张载之学,一个是胡宏之学。张载写《正蒙》,强调气化之性的重要性。他在《太和》篇中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8],这段话很重要。所谓人之性者,其所成由天道而来,天道又是由太虚通过气化而产生的一种运行,这种运行又与具有本体性的“虚”,即太虚之气相合,亦即由天道之动产生万物的品类流行,可谓为生生之性。对于人而言,“性”有了本体性也是个体性的潜能,以万物为机缘,才有一种知觉,才产生了“心”。
以张载作为论性的开始,才能更好地说明二程对天理的突出认识。大程认为,事物之所以成其然,莫非天理,对天理的体验是心对品类万物与天道流行的最大感受。天理可说包含在天道之中,使万物终于成为宇宙中的品类,而心作为觉知与感应之体,才能觉知而体验天道的万物,产生天理的概念。所谓天理者乃事物自然而必然的存在状态。当然,二程并没有就这个宇宙的本体处说起,而是就人的心性的体验来理会,即“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9],兹亦合乎所谓“天命之谓性”者。“性”就是天之所命,亦可谓是道之化成。有了这个背景之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二程所谓的性,中间已经有理的成分,也有气的成分,亦有天道的成分。所以“性”是事物存在的枢纽。后来胡五峰对此有所发挥,乃谓事物必须就“性”而谈,舍之则无法论物。此中包含了一种传承:张载影响二程,二程影响胡五峰。再者,上文谓小程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个“中”实际上就是“性”,而此“性”也可以说为张载所说合乎理之气化本体原始和谐状态。朱子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所可知的是:胡五峰是杨时的弟子,杨时又是二程的弟子,从杨时到胡五峰之思虑传承重点均放在对性的体悟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虽然《论语》中所谓性与天道是夫子所不多谈的,但夫子并非完全没有相应的观点。要解决性与天道的问题,就必须在此致力。这种探讨要经过一种体悟、体察、体会,再把它变成一种察识,实际上是体悟人性之“中”,然后发挥人性之“和”的实践之工夫。[10]朱子欲论性之本体,就必须要对“‘心’如何主导‘体’”的问题具备一种重新的认识。故他乃不得不面向湖湘学派进行探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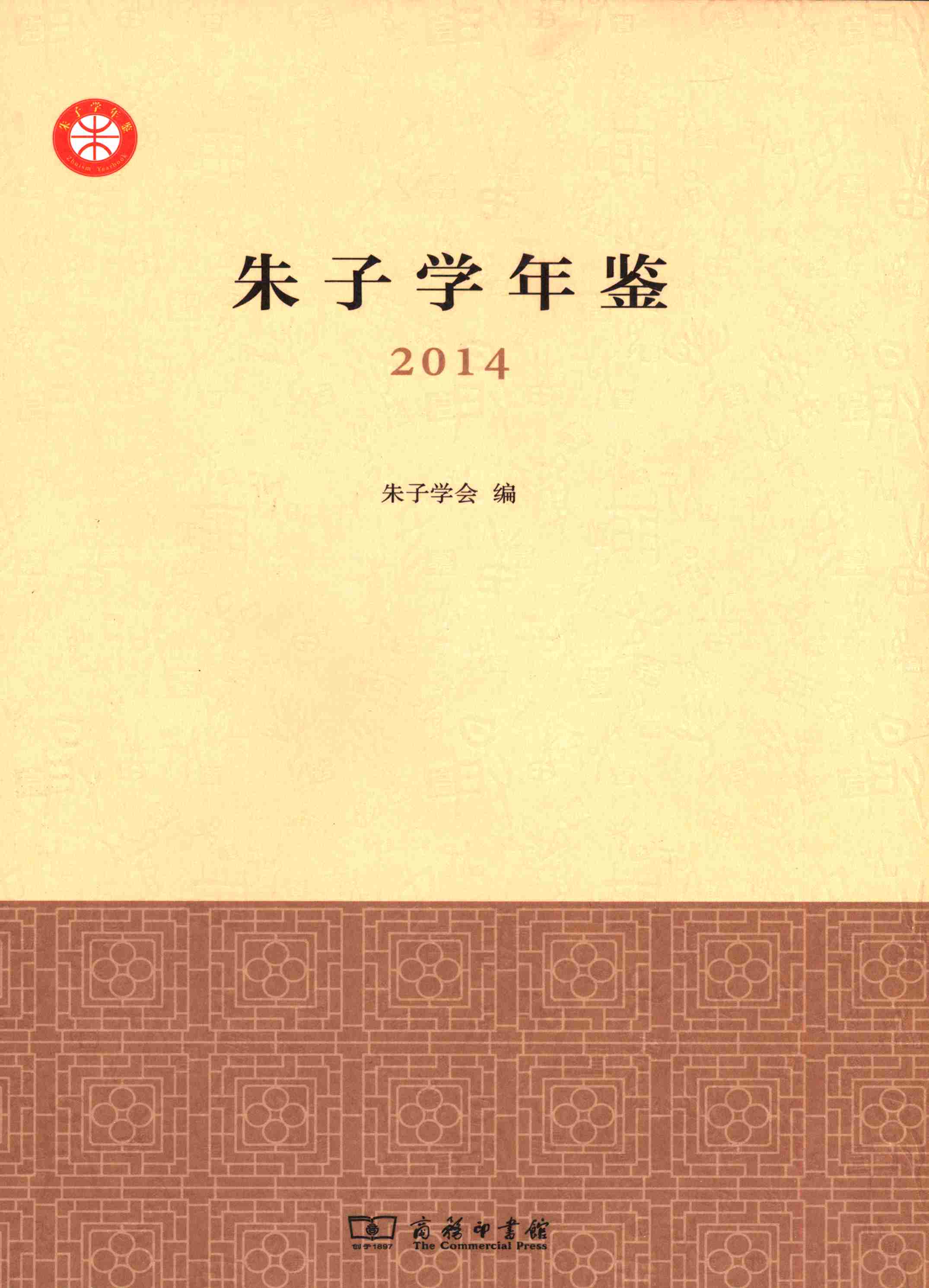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4》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分为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等九个栏目,收录了《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