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思孟学派的心性论解读“明德”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402 |
| 颗粒名称: | 三、以思孟学派的心性论解读“明德”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3 |
| 页码: | 106-108 |
| 摘要: | 该段文本主要探讨了朱熹对《大学》中"明德"的心性论内涵的思考,并通过引用孟子的观点和朱熹自己的解释来说明他对"明德"的理解。朱熹认为"明德"是通过个体的心性修养而成己成物的理论价值,同时将"明德"与心性、性、德等概念进行关联和解释。 |
| 关键词: | 明德 心性 孟子 |
内容
《大学》文本本身对“明德”的内涵没有具体的论述,更没有作出深入的心性论探讨。朱熹要对《大学》的为学工夫做出深入探讨,揭示其通过个体的心性修养而成己成物的理论价值,就必须对“明德”的心性论内涵做出思考。
在儒家经典中,《孟子》以心性论的深刻思考而为朱熹所特别重视。所以,朱熹对“明德”的思考,一直是以《孟子》为理论依据的。朱熹早年已经认识到“明德”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亦即认为人人皆有“明德”,最初也曾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他指出“明德”同“良心”一样,非由外铄,而是根于人心,被人的私欲所蔽而不明。他说:
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
此条是廖德明所录,时间在1186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仍然重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及其与《大学》“明德”之间的思想关联,但主要是从“明德”与“良知良能”都是人所固有,为天所赋予的相同特性加以考虑。显然,“良知良能”只是一个基于观察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还不足以揭示《大学》中“明德”的意蕴,更不能与精密严谨、系统深刻的佛教的心性论抗衡。他还必须继续追问“良知良能”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位阶,才能明了“明德”的内涵。
“明德”的内涵既然与心性问题紧密关联,要阐释“明德”的内涵,就必须要辨明心性与“明德”的关系。在《经筵讲义》中,朱熹将“明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直接以“性”释“明德”。但这又与《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有差异,因为《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是个“浑全”的事物,不仅仅是指内在的“德性”,也指能彰显于行动的德行,因而,是经由人的思想认识的结果,而思想认识是由“心”来承担的,所谓“心之官则思”。朱子也指出“心者,气之精爽”,“心官至灵,藏往知来”。所以他知道,单独以“性”释“明德”并不妥当。《朱子语类》记载: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徳’否?”
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6]
这是门人余大雅直接以朱熹的原话求证于朱熹,表明余大雅对朱熹将“明德”与心性相联系而产生了许多疑问。在这里,朱熹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表明了他在揭示“明德”内涵时的问题意识所在。他指出,“明德”是“感应虚明”的,因而“心之意亦多”;同时他也注意到,孟子总是将心与性联系起来论说的特点。
实际上,朱熹1189年所修订的《大学章句》中,对“明德”的注释,是不判分心德,即从心性一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此二句是说心?说德?”
曰:“心、德皆在其中,更仔细看。”
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
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7]
本条是徐寓于1190年至1191年之间,在漳州问学朱熹时所记,其中《大学注》指朱熹1189年修订的《大学章句》,1191年刊刻于漳州学宫。显然,《大学注》中,“其体”之“其”是指“明德”,“虚灵不昧”是对“明德”的本质特征的描述,也是对“明德”之“明”字内涵的揭示;“鉴照不遗”是言“明德”之用。在这条注释中,朱熹显然是以心释“明德”。“虚灵不昧”、“鉴照不遗”实际上就是心之体与用。但以“虚灵不昧”言“明德”之“体”,等于直接说心就是“明德”之“体”,但是他又指出“明德”是人心中“许多道理”。人之心合理气、统性情,故而德性必蕴涵于心,德行亦必为心之发。由心言明德,才能整全而无所偏废,但又必须兼性而言,否则,“明德”亦没有本原。在最终定论,即通行本《大学章句中》,朱熹回到孟子兼心言性、兼性言心的立场,指出人之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以“人之所得乎天”、“具万理”阐释“性”之明,以“虚灵不昧”、“应万事”阐明“心”之明,合心与性,而阐释“明德”之内涵。可见,朱熹注释“明德”,是兼心性为一体而言的。
又,人禽之辨是孟子提出的重要课题,但孟子的目的在于强调“仁义”的价值与基于仁义的内在人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8]史次耘先生指出,《孟子》此章的主旨是“强调人性本善,君子全顺自然之性而由仁义行。”[9]到了宋儒这里,则发展为探究人的本质,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是什么的问题。朱熹总结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其后学的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禽之差异的根源。他注释孟子的人禽之辨说: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尔。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10]
朱熹认为,从人物的化生来看,人与物之理是相同的,这是万物一体、人能与天合一的依据。人物之界分主要在禀受的气不同,人得气之正且通者,而物得气之偏且塞者。所以人能全其性,明天理,自觉按照天理行事,而物则不能。放到《大学》中来看,人禽之异或者说人物之界分就是人具有明德,而物没有。在《大学或问》中,朱熹指出:
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是则所谓明德者也。11]
实际上,朱熹说“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已经强调“明德”是人所有,含有界分人物之内涵,而“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从而使人能识其本性进而全齐本性,则是人的本质——人的规定性所在。可见,在这里,朱熹又以孟子兼说心性的方式阐明了明德作为人物界分的意义,从而深化了孟子的人禽之辨,使孟子的人禽之辨由强调人性本善的论据上升为探讨人的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命题。
我们发现,朱熹既以《孟子》诠释《大学》,又以《大学》诠释《孟子》,这取决于那部经典的长处和特点。在工夫论方面,他更认同《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对人格形成的作用,所以他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来诠释《孟子》中的“养气”、“尽性”。他说:“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诐、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12]但是在心性论方面他更认同《孟子》,故而他在心性论方面以《孟子》诠释《大学》。这样,既保证了他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尊重态度,又满足了不同儒学典籍的整合要求。从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来说,这是“蕴谓”层次,即朱熹在思考《大学》可能蕴涵的是什么。在这一层面朱熹已跳出文本本身,而采取“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他以《孟子》的心性思想回答《大学》蕴涵的心性论是什么。
在儒家经典中,《孟子》以心性论的深刻思考而为朱熹所特别重视。所以,朱熹对“明德”的思考,一直是以《孟子》为理论依据的。朱熹早年已经认识到“明德”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亦即认为人人皆有“明德”,最初也曾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他指出“明德”同“良心”一样,非由外铄,而是根于人心,被人的私欲所蔽而不明。他说:
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
此条是廖德明所录,时间在1186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仍然重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及其与《大学》“明德”之间的思想关联,但主要是从“明德”与“良知良能”都是人所固有,为天所赋予的相同特性加以考虑。显然,“良知良能”只是一个基于观察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还不足以揭示《大学》中“明德”的意蕴,更不能与精密严谨、系统深刻的佛教的心性论抗衡。他还必须继续追问“良知良能”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位阶,才能明了“明德”的内涵。
“明德”的内涵既然与心性问题紧密关联,要阐释“明德”的内涵,就必须要辨明心性与“明德”的关系。在《经筵讲义》中,朱熹将“明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直接以“性”释“明德”。但这又与《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有差异,因为《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是个“浑全”的事物,不仅仅是指内在的“德性”,也指能彰显于行动的德行,因而,是经由人的思想认识的结果,而思想认识是由“心”来承担的,所谓“心之官则思”。朱子也指出“心者,气之精爽”,“心官至灵,藏往知来”。所以他知道,单独以“性”释“明德”并不妥当。《朱子语类》记载: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徳’否?”
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6]
这是门人余大雅直接以朱熹的原话求证于朱熹,表明余大雅对朱熹将“明德”与心性相联系而产生了许多疑问。在这里,朱熹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表明了他在揭示“明德”内涵时的问题意识所在。他指出,“明德”是“感应虚明”的,因而“心之意亦多”;同时他也注意到,孟子总是将心与性联系起来论说的特点。
实际上,朱熹1189年所修订的《大学章句》中,对“明德”的注释,是不判分心德,即从心性一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此二句是说心?说德?”
曰:“心、德皆在其中,更仔细看。”
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
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7]
本条是徐寓于1190年至1191年之间,在漳州问学朱熹时所记,其中《大学注》指朱熹1189年修订的《大学章句》,1191年刊刻于漳州学宫。显然,《大学注》中,“其体”之“其”是指“明德”,“虚灵不昧”是对“明德”的本质特征的描述,也是对“明德”之“明”字内涵的揭示;“鉴照不遗”是言“明德”之用。在这条注释中,朱熹显然是以心释“明德”。“虚灵不昧”、“鉴照不遗”实际上就是心之体与用。但以“虚灵不昧”言“明德”之“体”,等于直接说心就是“明德”之“体”,但是他又指出“明德”是人心中“许多道理”。人之心合理气、统性情,故而德性必蕴涵于心,德行亦必为心之发。由心言明德,才能整全而无所偏废,但又必须兼性而言,否则,“明德”亦没有本原。在最终定论,即通行本《大学章句中》,朱熹回到孟子兼心言性、兼性言心的立场,指出人之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以“人之所得乎天”、“具万理”阐释“性”之明,以“虚灵不昧”、“应万事”阐明“心”之明,合心与性,而阐释“明德”之内涵。可见,朱熹注释“明德”,是兼心性为一体而言的。
又,人禽之辨是孟子提出的重要课题,但孟子的目的在于强调“仁义”的价值与基于仁义的内在人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8]史次耘先生指出,《孟子》此章的主旨是“强调人性本善,君子全顺自然之性而由仁义行。”[9]到了宋儒这里,则发展为探究人的本质,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是什么的问题。朱熹总结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其后学的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禽之差异的根源。他注释孟子的人禽之辨说: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尔。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10]
朱熹认为,从人物的化生来看,人与物之理是相同的,这是万物一体、人能与天合一的依据。人物之界分主要在禀受的气不同,人得气之正且通者,而物得气之偏且塞者。所以人能全其性,明天理,自觉按照天理行事,而物则不能。放到《大学》中来看,人禽之异或者说人物之界分就是人具有明德,而物没有。在《大学或问》中,朱熹指出:
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是则所谓明德者也。11]
实际上,朱熹说“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已经强调“明德”是人所有,含有界分人物之内涵,而“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从而使人能识其本性进而全齐本性,则是人的本质——人的规定性所在。可见,在这里,朱熹又以孟子兼说心性的方式阐明了明德作为人物界分的意义,从而深化了孟子的人禽之辨,使孟子的人禽之辨由强调人性本善的论据上升为探讨人的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命题。
我们发现,朱熹既以《孟子》诠释《大学》,又以《大学》诠释《孟子》,这取决于那部经典的长处和特点。在工夫论方面,他更认同《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对人格形成的作用,所以他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来诠释《孟子》中的“养气”、“尽性”。他说:“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诐、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12]但是在心性论方面他更认同《孟子》,故而他在心性论方面以《孟子》诠释《大学》。这样,既保证了他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尊重态度,又满足了不同儒学典籍的整合要求。从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来说,这是“蕴谓”层次,即朱熹在思考《大学》可能蕴涵的是什么。在这一层面朱熹已跳出文本本身,而采取“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他以《孟子》的心性思想回答《大学》蕴涵的心性论是什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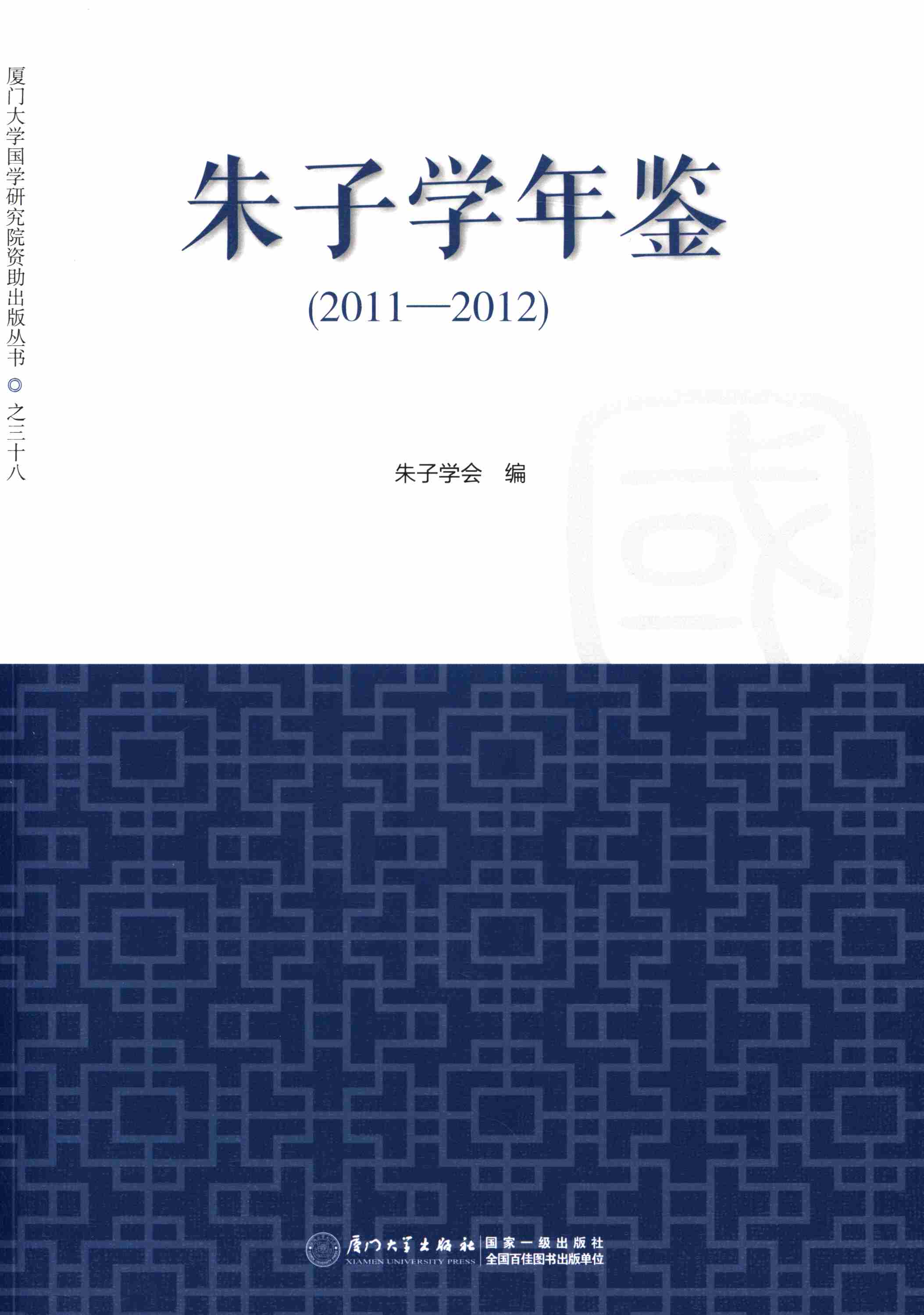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2011-2012年朱子学年鉴。内容包括本刊特稿2篇、朱子学研究新视野7篇、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6篇、朱子学研究新著38篇、朱子学书评3篇、朱子学研究优秀硕博士论文82篇、朱子学研究论文荟萃54篇、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4篇、朱子学国内外学术动态6篇、朱子学研究机构介绍3篇、朱子学研究学者介绍13篇、2011-2012年朱子学新书索引、2011-2012年朱子学论文索引556篇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