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396 |
| 颗粒名称: | 四、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5 |
| 页码: | 85-89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强调主敬工夫是为了收敛身心,将心放在一个“模匣子”里面,以便随事逐物地思考道理。他认为人心本来是光明的,但容易被利欲等影响而变昏暗。他强调通过敬来降伏心,使心能在义理上安顿,不被物欲所迷惑,而能正确认识事物。朱熹指出敬是为学的根本大法,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等一切工夫都从敬出发。然而,朱熹也指出敬并不是放任不顾的意味,而是要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他强调要在应事接物中发挥集义的工夫,防止心境的浮躁。朱熹认为主敬与居敬交相为用,通过集义的功夫可以更好地实践敬的作用,但敬仍然是首要的方法。最后,朱熹强调敬与义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可以达到达到天德的境界。 |
| 关键词: | 心地光明 收敛身心 主敬工夫 |
内容
按照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等命题来看,敬是令此心“作主”、“自存”、“常存”的保证,但不能倒过来说,以心为敬作主。与此思路一致,朱熹还有一个重要说法,即“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而且朱熹将此提到了“为学”之“大要”的高度来加以肯定,换言之,以敬收心,可谓是朱子学的为学宗旨。他说:
为学有大要。若论看文字,则逐句看将去。若论为学,则自有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个敬字与学者说。要且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缉如缉麻之缉,连缉不已之意。熙则训明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今释氏自谓光明,然父子则不知其所谓亲,君臣则不知其所谓义,说他光明,则是乱道。[61]
这是说,做学问是有根本方法的,如果读书,可以逐字逐句地读,但若是说做学问,则自有根本之法,这就是程子向学者所说的“敬”。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要而言之,就是要用“敬”来收敛身心,如同把身心放在一个“模子”里面那样,能使身心运作不走样,然后随事就物上去穷究事物之理。朱熹接着说:就本来意义上而言,心地原是“光明”的,本无污染,犹如人见他人做得对便说对,做得不对便说不对那样,心里面的是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人心易受后天环境的不良影响,染上利欲熏心等毛病,使得心地昏暗了。至于佛教所说的“光明”则全不着地、脱离事物,如父子不知亲、君臣不知义,这种所谓的心地“光明”最为危险可怕。
朱熹在这里所欲表明的观点有互为关联的两层意思:第一,为学大要在于以敬之工夫来收敛身心;第二,这是由于人心“才明便昏了”的缘故。至于另一层意思——心地原是光明,则不是主敬工夫的前提设定。朱熹的思路是:心地虽然原本光明,但不可以光明之心去主导敬之工夫,否则的话,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形上的、普遍的、永恒的心之本体或道德本心的存在。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光明”只是就心地的原初意义上而言,而非就心地的超越意义上立论。要之,不能在主敬工夫之前之上预设心之本体的存在,这是朱熹不可退让的原则立场,他之所以强烈反对湖湘学的“以心观心”(当然这是朱熹的诠释而不一定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内涵)并将其喻作佛教的“以心求心”,其思想缘由便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说的“放在模匣子里面”的比喻性说法非常生动有趣,这是由于朱熹很担心“身心”容易脱离轨道、胡乱运作,故有必要用“模匣子”来规范它、约束它。这个“模匣子”就是比喻“敬”,由此推论,由“敬”摄心便是指知觉层面上的人心而不能是道德层面上的本心。例如朱熹还有一些说法,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62]
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63]
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64]
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在这里截然。……常常恁地收拾得这心在,便如执权衡以度物。[65]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66]
这里所说的“降伏”、“收拾”、“收敛”、“绳检”等动词的主体都是“敬”,相对地说,“心”则是“敬”的客体对象。要把心安顿下来,安顿在“义理上”,便是主敬工夫的主要任务。其云去“物欲”存“义理”而令此心不至于“东走西走”、“胡思乱想”,亦是将心之状态规定为敬之工夫的对象。正是通过上述“收拾”、“收敛”等等主敬工夫的程序,然后才能实现人心为主(“万事之主”)的目标,朱熹喻作“如执权衡以度物”,意谓由敬摄心,方能使此心成为“度物”之标准。也正由此,所以朱熹说敬既是“一心之主宰”又是“万事之本根”,不能倒过来说,心是敬之主宰。其云“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67],亦同此义,意谓敬才是存心养性的根本方法而不是相反。由此出发,故朱熹说,敬是为学之根本大法,是圣学第一义之工夫。朱熹断然指出: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68]
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69]
其中的“据依”亦即“依据”。这是说,“敬之一字”乃是“涵养省察,格物致知,如种种功夫”的依据。但须指出的是,此所谓“依据”,只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本源之意而非就本体论而言的理据之意,换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各种工夫方法虽然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一个根本的方法,那就是主敬,显然这是平铺地说主敬是一切工夫的“据依”,而不是形上地说“敬”是心性之“理据”,因为“敬”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不过令人注意的是,朱熹的上述说法涉及主敬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敬与集义、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这里须稍加考察。
由上所述,主敬工夫主要是指向人心而言,属于一种内心之工夫,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如果说只要“守定一个敬字”,便可一了百了,于应事接物亦可全然不顾,则非但不是朱熹之主张,而正是朱熹所批评的偏见。他指出: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70]
若学者,当求无邪思,而于正心诚意处着力。然不先致知,则正心诚意之功何所施?所谓敬者,何处顿放?今人但守一个“敬”字,全不去择义,所以应事接物处皆颠倒了。[71]
这里以“随事专一”言“敬”,表明主敬工夫必落在“事”上,也就是后一段所强调的在“应事接物处”做一番“集义”工夫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朱熹常常用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来加以强调,他说:“敬义夹持,循环无端。”[72]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夹持”关系呢?朱熹有一个解释,可谓曲尽其详:
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虚骄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则恐亦未免于昏愦杂扰,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谓集义,正是要得看破那边物欲之私,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头头处处,无不如此体察,触手便作两片,则天理日见分明,所谓物欲之诱,亦不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但更得集义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盖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无昏愦杂扰之病。……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谈义、去本逐末,正欲两处用功,交相为助,正如程子所谓“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者耳。[73]
在这里,朱熹强调居敬与集义交相为用的观点,不过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熹还是坚持“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的观点,这是朱熹己丑之悟后所坚持的“日用本领工夫”的一贯立场,不容改变。
朱熹还用“互相发”的说法来解释居敬与穷理的关系: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74]
问题是这种“互相发”的工夫,何者更为根本?从上述这段话的字面来看,朱熹只是说两者互以他者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亦即两者是平行的关系,而其最后一句“其实只是一事”,则意谓两种工夫其实只是同一个工夫的过程。这一思维方式,颇类似于朱熹的“知行并进”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有讨论,这里须指出这一并行关系的两种工夫虽同处在一个工夫过程中,可以说穷理离不开居敬,也可说居敬离不开穷理,但是只有居敬工夫具有贯动静、通上下、成始终、无间断、常惺惺之特征,显然比穷理工夫更为根本。故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工夫论问题上,以主敬为第一义,穷理为第二义,亦不无道理。[75]如朱熹曾说:
为学两途,诚如所喻。然循其序而进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谓存心者,非拘执系缚而加桎梏焉也。盖尝于纷扰外驰之际,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长,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间,则是心也,其庶几乎![76]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虽然没有提到“敬”字,但我们却可以将此放在“敬”的脉络下来观察朱熹有关心物关系问题的立场。从其表述看,存心与格物并存不悖、相互为用,故谓“一而已矣”,然而心若不存,则格物工夫亦无可下手,显然存心较诸格物更为根本。如朱熹曾明确指出:
《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77]
至于如何存心,朱熹强调只是在一念之间,一觉此心,则此心在也,其间容不得丝毫的智力安排。其实,这里的“觉”字,便是敬字工夫的提撕义。关于觉、心、敬的彼此关联,我们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觉底是敬,觉处即心[78]。要之,存心其实就是由居敬工夫“一觉此心”之意。重要的是,由“一觉此心”便可令此心自在(“即此而在”),而觉此心者端在于敬字工夫,此即朱熹再三强调的主敬可使“自心自省”之意,也就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之意。
最后顺便指出,在有关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曾有这样一个定义:“敬则心之贞也。”[79]这是说,敬就是指心之贞定。按,此《答张钦夫书》非常著名,即所谓“诸说例蒙印可”书,为朱熹40岁时所作,然清儒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于“38岁”条却谓“后来都无此语”,意指该说为朱熹未定之论,不明理由何在。牟宗三则断定王说为非,并对“敬则心之贞也”有所肯定:“此语实甚佳。在朱子系统中,其意即是心气之贞定与凝聚,非从本体性的超越心而言也。”并说:“此义亦不悖于朱子静涵静摄之系统”[80]。可以看出,牟氏之肯定是顺着朱熹而说,若依牟氏之判教立场而言,则此“静涵静摄”盖谓朱熹思想之特质为理“存有而不动”,其动者为心气,而这一点正是牟氏所不能认同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于朱熹之主敬则不可以“静”字概之,朱熹所言主敬工夫意义上的“自心自省”之“心”亦非“心气”一词可以概之。诚然,由“敬则心之贞也”之命题的内涵来看,心是敬之对象,此即朱熹所言由敬摄心的题中应有之意,若此,则心莫非是现象实然之存在而可归于“气”之范畴?关于心是否就是气的问题,上引拙文已有讨论,这里不必赘述。要而言之,至少在朱熹敬论的思想脉络中,由敬而提撕唤醒之心乃是一“为主”而不“为客”之存在[81],绝非“心气”一词所能涵盖。朱熹所用的“心气”一词,例如:“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82],“心平气和”、“心气和平”[83]等等,均是日常语言所说的心平气和之意,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意涵。事实上,如何结合朱熹所说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来看,那么“敬则心之贞也”便不难理解,其意无非是说敬能令此心“贞定”而发挥“主宰”之作用。
为学有大要。若论看文字,则逐句看将去。若论为学,则自有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个敬字与学者说。要且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缉如缉麻之缉,连缉不已之意。熙则训明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今释氏自谓光明,然父子则不知其所谓亲,君臣则不知其所谓义,说他光明,则是乱道。[61]
这是说,做学问是有根本方法的,如果读书,可以逐字逐句地读,但若是说做学问,则自有根本之法,这就是程子向学者所说的“敬”。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要而言之,就是要用“敬”来收敛身心,如同把身心放在一个“模子”里面那样,能使身心运作不走样,然后随事就物上去穷究事物之理。朱熹接着说:就本来意义上而言,心地原是“光明”的,本无污染,犹如人见他人做得对便说对,做得不对便说不对那样,心里面的是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人心易受后天环境的不良影响,染上利欲熏心等毛病,使得心地昏暗了。至于佛教所说的“光明”则全不着地、脱离事物,如父子不知亲、君臣不知义,这种所谓的心地“光明”最为危险可怕。
朱熹在这里所欲表明的观点有互为关联的两层意思:第一,为学大要在于以敬之工夫来收敛身心;第二,这是由于人心“才明便昏了”的缘故。至于另一层意思——心地原是光明,则不是主敬工夫的前提设定。朱熹的思路是:心地虽然原本光明,但不可以光明之心去主导敬之工夫,否则的话,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形上的、普遍的、永恒的心之本体或道德本心的存在。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光明”只是就心地的原初意义上而言,而非就心地的超越意义上立论。要之,不能在主敬工夫之前之上预设心之本体的存在,这是朱熹不可退让的原则立场,他之所以强烈反对湖湘学的“以心观心”(当然这是朱熹的诠释而不一定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内涵)并将其喻作佛教的“以心求心”,其思想缘由便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说的“放在模匣子里面”的比喻性说法非常生动有趣,这是由于朱熹很担心“身心”容易脱离轨道、胡乱运作,故有必要用“模匣子”来规范它、约束它。这个“模匣子”就是比喻“敬”,由此推论,由“敬”摄心便是指知觉层面上的人心而不能是道德层面上的本心。例如朱熹还有一些说法,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62]
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63]
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64]
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在这里截然。……常常恁地收拾得这心在,便如执权衡以度物。[65]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66]
这里所说的“降伏”、“收拾”、“收敛”、“绳检”等动词的主体都是“敬”,相对地说,“心”则是“敬”的客体对象。要把心安顿下来,安顿在“义理上”,便是主敬工夫的主要任务。其云去“物欲”存“义理”而令此心不至于“东走西走”、“胡思乱想”,亦是将心之状态规定为敬之工夫的对象。正是通过上述“收拾”、“收敛”等等主敬工夫的程序,然后才能实现人心为主(“万事之主”)的目标,朱熹喻作“如执权衡以度物”,意谓由敬摄心,方能使此心成为“度物”之标准。也正由此,所以朱熹说敬既是“一心之主宰”又是“万事之本根”,不能倒过来说,心是敬之主宰。其云“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67],亦同此义,意谓敬才是存心养性的根本方法而不是相反。由此出发,故朱熹说,敬是为学之根本大法,是圣学第一义之工夫。朱熹断然指出: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68]
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69]
其中的“据依”亦即“依据”。这是说,“敬之一字”乃是“涵养省察,格物致知,如种种功夫”的依据。但须指出的是,此所谓“依据”,只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本源之意而非就本体论而言的理据之意,换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各种工夫方法虽然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一个根本的方法,那就是主敬,显然这是平铺地说主敬是一切工夫的“据依”,而不是形上地说“敬”是心性之“理据”,因为“敬”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不过令人注意的是,朱熹的上述说法涉及主敬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敬与集义、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这里须稍加考察。
由上所述,主敬工夫主要是指向人心而言,属于一种内心之工夫,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如果说只要“守定一个敬字”,便可一了百了,于应事接物亦可全然不顾,则非但不是朱熹之主张,而正是朱熹所批评的偏见。他指出: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70]
若学者,当求无邪思,而于正心诚意处着力。然不先致知,则正心诚意之功何所施?所谓敬者,何处顿放?今人但守一个“敬”字,全不去择义,所以应事接物处皆颠倒了。[71]
这里以“随事专一”言“敬”,表明主敬工夫必落在“事”上,也就是后一段所强调的在“应事接物处”做一番“集义”工夫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朱熹常常用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来加以强调,他说:“敬义夹持,循环无端。”[72]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夹持”关系呢?朱熹有一个解释,可谓曲尽其详:
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虚骄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则恐亦未免于昏愦杂扰,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谓集义,正是要得看破那边物欲之私,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头头处处,无不如此体察,触手便作两片,则天理日见分明,所谓物欲之诱,亦不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但更得集义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盖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无昏愦杂扰之病。……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谈义、去本逐末,正欲两处用功,交相为助,正如程子所谓“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者耳。[73]
在这里,朱熹强调居敬与集义交相为用的观点,不过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熹还是坚持“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的观点,这是朱熹己丑之悟后所坚持的“日用本领工夫”的一贯立场,不容改变。
朱熹还用“互相发”的说法来解释居敬与穷理的关系: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74]
问题是这种“互相发”的工夫,何者更为根本?从上述这段话的字面来看,朱熹只是说两者互以他者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亦即两者是平行的关系,而其最后一句“其实只是一事”,则意谓两种工夫其实只是同一个工夫的过程。这一思维方式,颇类似于朱熹的“知行并进”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有讨论,这里须指出这一并行关系的两种工夫虽同处在一个工夫过程中,可以说穷理离不开居敬,也可说居敬离不开穷理,但是只有居敬工夫具有贯动静、通上下、成始终、无间断、常惺惺之特征,显然比穷理工夫更为根本。故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工夫论问题上,以主敬为第一义,穷理为第二义,亦不无道理。[75]如朱熹曾说:
为学两途,诚如所喻。然循其序而进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谓存心者,非拘执系缚而加桎梏焉也。盖尝于纷扰外驰之际,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长,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间,则是心也,其庶几乎![76]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虽然没有提到“敬”字,但我们却可以将此放在“敬”的脉络下来观察朱熹有关心物关系问题的立场。从其表述看,存心与格物并存不悖、相互为用,故谓“一而已矣”,然而心若不存,则格物工夫亦无可下手,显然存心较诸格物更为根本。如朱熹曾明确指出:
《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77]
至于如何存心,朱熹强调只是在一念之间,一觉此心,则此心在也,其间容不得丝毫的智力安排。其实,这里的“觉”字,便是敬字工夫的提撕义。关于觉、心、敬的彼此关联,我们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觉底是敬,觉处即心[78]。要之,存心其实就是由居敬工夫“一觉此心”之意。重要的是,由“一觉此心”便可令此心自在(“即此而在”),而觉此心者端在于敬字工夫,此即朱熹再三强调的主敬可使“自心自省”之意,也就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之意。
最后顺便指出,在有关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曾有这样一个定义:“敬则心之贞也。”[79]这是说,敬就是指心之贞定。按,此《答张钦夫书》非常著名,即所谓“诸说例蒙印可”书,为朱熹40岁时所作,然清儒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于“38岁”条却谓“后来都无此语”,意指该说为朱熹未定之论,不明理由何在。牟宗三则断定王说为非,并对“敬则心之贞也”有所肯定:“此语实甚佳。在朱子系统中,其意即是心气之贞定与凝聚,非从本体性的超越心而言也。”并说:“此义亦不悖于朱子静涵静摄之系统”[80]。可以看出,牟氏之肯定是顺着朱熹而说,若依牟氏之判教立场而言,则此“静涵静摄”盖谓朱熹思想之特质为理“存有而不动”,其动者为心气,而这一点正是牟氏所不能认同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于朱熹之主敬则不可以“静”字概之,朱熹所言主敬工夫意义上的“自心自省”之“心”亦非“心气”一词可以概之。诚然,由“敬则心之贞也”之命题的内涵来看,心是敬之对象,此即朱熹所言由敬摄心的题中应有之意,若此,则心莫非是现象实然之存在而可归于“气”之范畴?关于心是否就是气的问题,上引拙文已有讨论,这里不必赘述。要而言之,至少在朱熹敬论的思想脉络中,由敬而提撕唤醒之心乃是一“为主”而不“为客”之存在[81],绝非“心气”一词所能涵盖。朱熹所用的“心气”一词,例如:“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82],“心平气和”、“心气和平”[83]等等,均是日常语言所说的心平气和之意,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意涵。事实上,如何结合朱熹所说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来看,那么“敬则心之贞也”便不难理解,其意无非是说敬能令此心“贞定”而发挥“主宰”之作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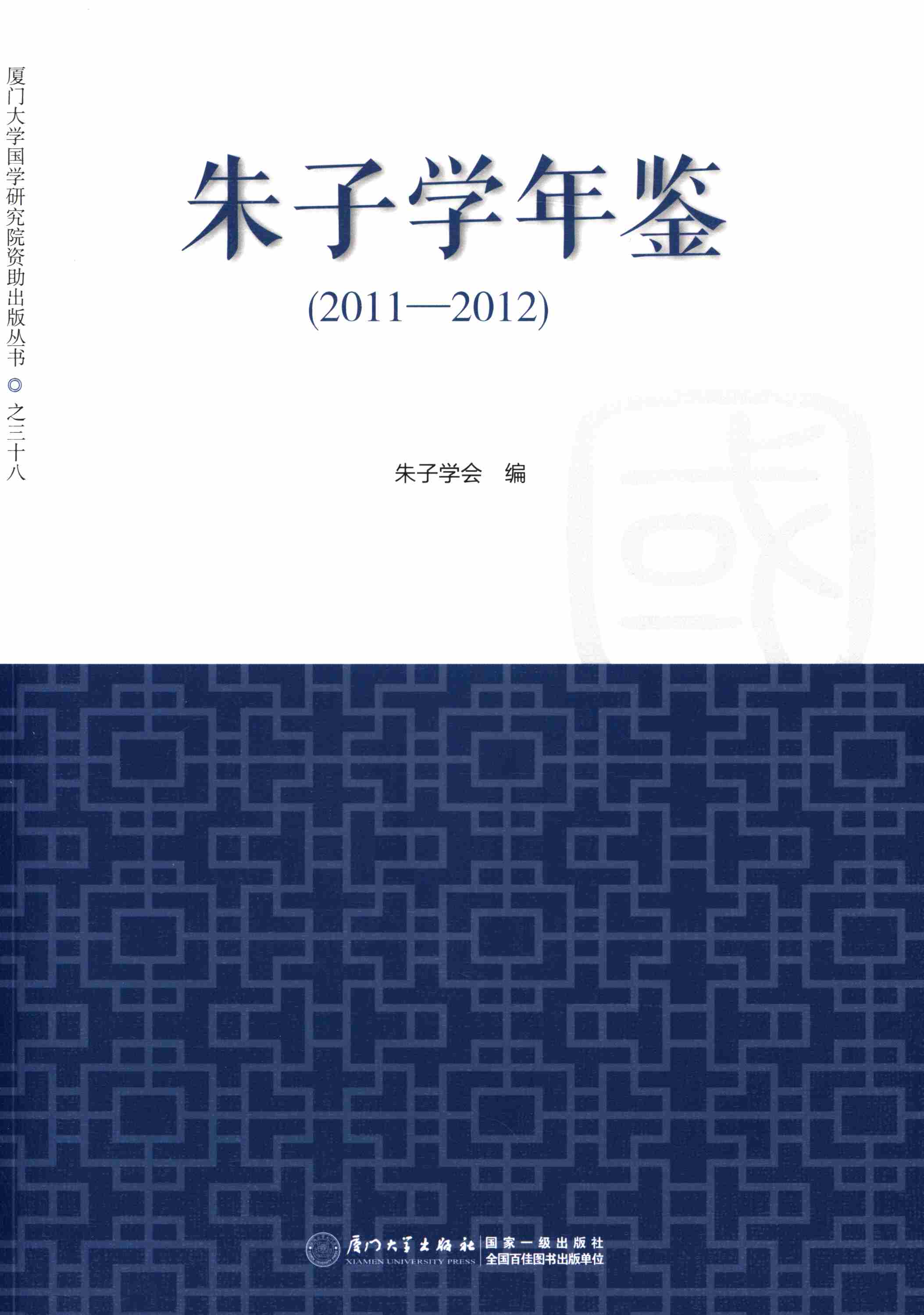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2011-2012年朱子学年鉴。内容包括本刊特稿2篇、朱子学研究新视野7篇、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6篇、朱子学研究新著38篇、朱子学书评3篇、朱子学研究优秀硕博士论文82篇、朱子学研究论文荟萃54篇、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4篇、朱子学国内外学术动态6篇、朱子学研究机构介绍3篇、朱子学研究学者介绍13篇、2011-2012年朱子学新书索引、2011-2012年朱子学论文索引556篇等。
阅读
相关人物
吴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