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371 |
| 颗粒名称: | 三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3 |
| 页码: | 41-43 |
| 摘要: | 该文集的第五八卷中收录了《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一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认为性是太极的整体,但其中包含了众多的理,而仁、义、礼、智是性中最重要的四大理。孟子发明了四端之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的理论。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四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仁和义的关系,最终强调了智的意义以及其与贞和元的联系。 |
| 关键词: | 性善 四端 仁义礼智 |
内容
《文集》卷五八载《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该信可分为四节,其开首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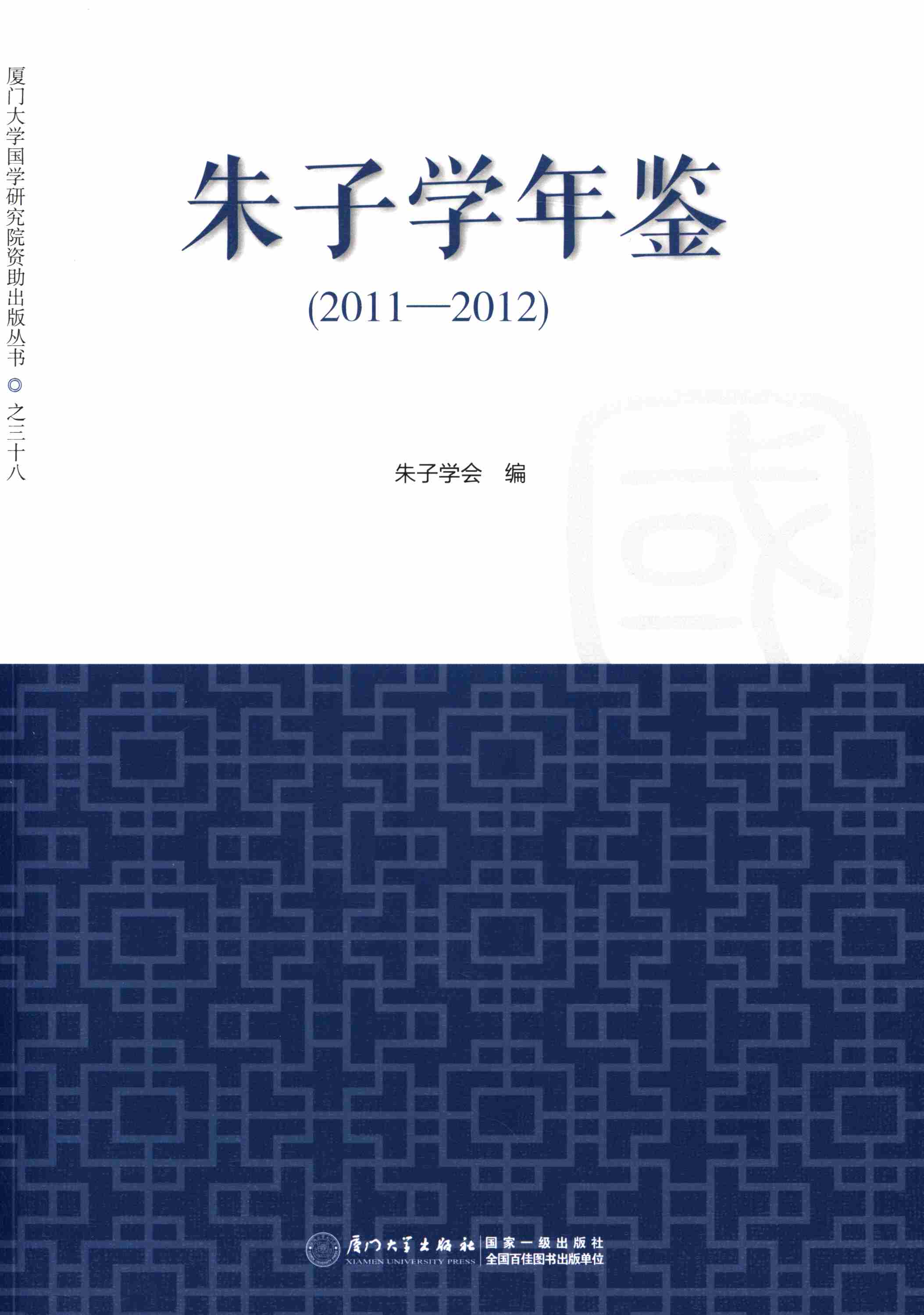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2011-2012年朱子学年鉴。内容包括本刊特稿2篇、朱子学研究新视野7篇、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6篇、朱子学研究新著38篇、朱子学书评3篇、朱子学研究优秀硕博士论文82篇、朱子学研究论文荟萃54篇、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4篇、朱子学国内外学术动态6篇、朱子学研究机构介绍3篇、朱子学研究学者介绍13篇、2011-2012年朱子学新书索引、2011-2012年朱子学论文索引556篇等。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来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