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四德说续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368 |
| 颗粒名称: | 朱子四德说续论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38-51 |
| 摘要: | 本文从《朱子语类》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的资料出发,探讨了朱子关于仁义礼智四德的观点。通过分析《元亨利贞说》、《周礼三德说》、《仁说》、《玉山讲义》以及《周易本义》中对仁义礼智的论述,揭示了朱子对于四德的理解和思考。 |
| 关键词: | 朱子思想 四德论 仁义礼智 |
内容
在《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一文中,我们主要是利用《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的资料来说明朱子的关于仁义礼智四德(以及与之关联的元亨利贞四德)的思想。[1]这里,我们依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简称《文集》)、《朱子语类》(下简称《语类》)的其他材料来进一步讨论其四德说,主要使用《文集》中的《元亨利贞说》、《周礼三德说》、《仁说》,《玉山讲义》及相关讨论,以及《语类》及《周易本义》论《易·乾卦》的资料。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有《元亨利贞说》,文云: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2]
《元亨利贞说》写于朱子四十二岁前后,属于其前期思想。朱子当时以元亨利贞四者为性,与生长收藏相对待;这和以仁义礼智为性、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是相对应的也是一致的。元亨利贞是天地之性,天地之化以天地之性为根据,而实现生长收藏的过程。同理,仁义礼智是人之性,人心之动以人之性为根据,而发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这种分析体现了朱子当时对性情之辨的重视。在这种话语中,元亨利贞只是性,与生长收藏的现实过程被严格分别开来,生长收藏相当于情,也就是用。
不久,朱子又有《仁说》之作,其中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
依朱子这里的看法,仁是“人心”之德,元亨利贞是“天地之心”之德,这是明确把仁和元、亨、利、贞都作为“德”。就心之德作为性而言,“元”包“亨利贞”,这是从体上来看的。朱子还认为,四季运行是天地之化的过程,是用,而天地之德则是运行过程的内在根据。从天地运行的大用着眼,春生之气贯通于春夏秋冬的有序连接,无所不通。如果从人的方面看,就心之徳言,“仁”包“义礼智”;就四德的发用言,恻隐贯通于爱恭宜别四种情感。在这种论述中,春生之气相当于恻隐,都属用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运行、流行是就“用”言,而仁义礼智或元亨利贞是“体”,是“性”,是无所谓流行的。既然性无所谓流行,这说明前期朱子思想在性情体用之辨的意识主导下,不采用“流行”一类的观念解释四德。我们在前文已说明,以“流行”的观念解释四德关系,见于朱子后期思想,而“运用流行”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和气的哲学思维分不开的。从哲学上看,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性和情两者的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总体的了解,这就是所谓“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心不是本性、体,也不是过程、用,而是包涵体用的、存在与活动的总体。
二
《文集》卷七四有《玉山讲义》,是朱子晚年六十五岁经过江西玉山时所作,其中论述了四德说。此讲义可分为三部分,其第一部分云:
时有程珙起而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4]
程珙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孔子只说仁,不说仁义,因为孔子说仁是讲元气;而孟子说仁义,是讲阴阳二气。这个讲法其实合于朱子晚年以仁为生气流行贯通四者的思想。程珙还把仁义的关系理解为体用的关系。朱子认为他讲的不分明,强调“仁义”二字的前提先要从人性论上去理解。天赋予每个所生之物一个道理,人身得到的这个道理便是性,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以这五种都是人性的道理。就五者都是人性的内容而言,彼此并无体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仁是体、义是用。
其第二部分云:
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5]
“仁是温和慈爱的道理”,道理即理,道理之在我者即性,说明这里是把“仁”作为理看待的。所谓温和慈爱的道理,与《四书章句集注》所说“仁者爱之理”[6]的意思相通,也就是说,“仁”是发为慈爱的内在根据。慈爱是已发而为用的,属于发见的层次;仁则是体,是未发的层次。义、礼、智皆然。仁义礼智之间的分别,亦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发见不同,仁发为慈爱,义发为断制,礼发为恭敬,智发为是非。“仁”是发为慈爱的根据道理,“义”是发为断制的根据道理,“礼”是发为恭敬的根据道理,“智”是发为是非的根据道理。但朱子晚年并不简单直截地说仁是恻隐之理,义是羞恶之理,礼是恭敬之理,智是是非之理,而常常说“仁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截割底道理”等,表示朱子的这种“道理”的表述还是有其特殊意义,这就是,朱子这时已经常常用“意思说”来表达其四德说了(详见前文)。此外,在这种说法中,朱子所体现的态度是即用明体、即用论体、不可离用说体,这与体用分析的说法有别。
第三部分云:
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着,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功夫处矣。”[7]
这里就用了“意思说”,强调仁是生的意思,即仁作为“生意”的思想。朱子认为仁之生意通贯周流于仁义礼智四者之中,初看起来,仁之生意贯通的讲法似是指仁的普遍性,而以四者为特殊性;其实这种“通贯周流”的讲法与普遍性体现为特殊性的思维还是有所不同的,要言之,“通贯周流”是气论的表达方式。分别而言,仁是仁之生意的本体的表现,义是仁之生意表现为断制的阶段,礼是仁之生意的节文,智是仁之生意表现为分别。朱子认为,这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之中一样,朱子用这种周流贯通之气的流行论,发挥了程颢的生意说与程颐仁“包”四德的观念,使得“仁”也成为或具有流行贯通能力的实体。这样的仁,既不是内在的性体,又不是外发的用,而是兼体用而言的了。气论的思维在这里也明显发生作用。这些就与前期的思想有所不同了。朱子的这一思想与程珙所提的“仁是元气”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元气不如生气说得更清楚,“元气”必须落在“生”字上讲,这是二程到朱子的仁说所一直强调的。关于礼是仁之著,智是义之藏的说法,以及仁义的体用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结合《语类》再予讨论。
由此可见,《玉山讲义》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一个是四德与四端的未发已发说,一个是仁之生意流行于四德说。在稍后答陈器之书中,朱子复述了这两点,并对“对立成两”、“仁智终始”等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
三
《文集》卷五八载《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该信可分为四节,其开首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
四
《文集》卷六七有《周礼三德说》,该文虽然不是讨论四德之说,但其中讨论周礼三德说涉及的对德、行的理解也值得注意。文之开首云:
或问:师氏之官,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何也?曰:至德云者,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则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行”则理之所当为,日可见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恶,则以得于己者笃实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恶,而自不忍为者也。(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则赵无愧、徐仲车之徒是已。)凡此三者,虽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见其相须为用而不可偏废之意。盖不知至德,则敏德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则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陈备举而无所遗,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资、精粗两尽而不倚于一偏也。[13]
“三德”、“三行”之说出于《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4]这是古代德行论的早期表达。
朱子对三德、三行作了明确的哲学的、伦理学的解说。在朱子看来,以三种德行教国子,至德是指心而言,是关于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所谓至德以为道本,是说至德是掌握性命之理、践行当然之则、实行治国平天下之术的根本与基础,突出了德性对哲学理解、道德实践、政治施行的根本意义,强调心徳是道术的根本基础。强志力行,即《礼记·儒行》第一条所说的强学力行;一切行为都是由心志而发,人能强化心志,力行理所当为,使心志在行为事迹上表现出来,这是敏德。所谓敏德以为行本,是指由心志落实到行为是德行的一般特性。照朱子的这个说法,从德行论来看,可以说正心诚意是根本的德行,称为至德;强志力行是一般意义的德行,称为敏德;尊祖爱亲是专指孝的特殊德行,称为孝德。三徳可以说区别了根本德行、一般德行、特殊德行。
以三德教国子,说明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成人。但把国子培养为成人,必须使他们同时培养三德,不可偏专其中之一。朱子认为三德互相补充、互相需要,“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也就是说三德具有统一性。没有至德,敏德只能笃行,而没有方向,不能知“道”;没有敏德,至德就会流于空洞,无法具体落实,也无法拓宽事业;不落实到孝德,敏德就失去基础。至德是方向,敏德是分殊,孝德是基础。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盖不本之以其德,则无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实之以其行,则无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进。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继之,则虽其至末至粗亦无不尽,而德之修也不自觉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则无与焉。盖二者之行,本无常师,必协于一,然后有以独见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预言也。唯孝德则其事为可指,故又推其类而兼为友顺之目以详教之,以为学者虽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则进乎德而无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溯其原,则孰谓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乡三物之为教也亦然,而已详。[15]
三德之教和三行之教,涉及对德与行的分别。在对教三行的解释上,朱子解释了什么是德、行,他说“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这是说,“德”是得于心的状态或性质,“行”是对规范的实行。朱子认为,德和行互相支持、互相连接,不以内心之德为本,就达不到自得,行为也不能自修;心之德不落实在行为表现出来,心难以持循,心德也不能进步。朱子也指出,人有时未得于心,但能勉而行之,在这种状态下不能说德在心中。但如此勉而行之,久而久之,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不断实行便可使人达到“得于心”,即促使德在心中形成,这时的行为便是从心中之德出发,不待勉强了。这是朱子对德性形成的一种看法。
朱子还说过:
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泳。[16]
聪、明是耳目的根本属性,仁是心的根本属性,德即指根本属性而言。
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节。[17]
百行是行为,仁义礼智是本性,这是强调一切行为都是发自于内在的本性,也体现了朱子德性论强调性理的特色。
五
《周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8]此后,儒学思想家常常依此思路,努力把仁义与阴阳、刚柔对应起来,以建立宇宙论的统一性说明。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僴。[19]
理学倾向于把“阴阳”作为普遍的哲学分析方法。按照这种分析,如果把仁义礼智四者归为阴阳两类,那么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何者为阳,何者为阴?朱子的主张是,仁和礼属于阳,义和智属于阴。在他看来,以流行的次序而言,是仁、礼、义、智,也就是仁相当于春,礼相当于夏,义相当于秋,智相当于冬。因此若要把四德分为阴阳的话,仁、礼为阳,义、智为阴;正如要把一年四季分为阴阳的话,以春夏为阳,以秋冬为阴。反过来说,如果把四季分为仁义二者,则以春夏为仁,以秋冬为义。这种思维是汉代以来阴阳气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不过,这样一来,仁、礼、义、智的次序便和习惯所用的仁、义、礼、智的顺序有所不同了,朱子回答学生的疑问:
问:“孟子说仁义礼智,义在第二;《太极图》以义配利,则在第三。”曰:“礼是阳,故曰亨。仁义礼智,犹言东西南北;元亨利贞,犹言东南西北。一个是对说,一个是从一边说起。”夔孙。[20]
按朱子的理解,如同一个圆圈,顺着圆圈的次序是流行的次序,即仁、礼、义、智的排序。以流行言,仁对应元,礼对应亨,义对应利,智对应贞。如果不顺着圆圈,而以南北相对,东西相对,这样的次序就不是流行的次序,而是对待的次序,这就是仁、义、礼、智的排序。
问:“‘元亨利贞’,《乾》之四德;仁义礼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礼,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礼义智,犹言春夏秋冬也;仁义礼智,犹言春秋夏冬也。”铢。[21]
这也是说明四德有两种排序。仁、礼、义、智的顺序是合乎元气流行的自然次序,这样的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是被用气的流行来刻划的东西了,也就成为他所说的“流行之统体”了。
中国哲学中与“阴阳”分析相配合的是“刚柔”的分析。按上面的说法,仁属于阳,义属于阴,那么仁义与刚柔又如何对应呢?在一般人看来,仁有柔软的意思,应当属柔,不应当属刚,而朱子却认为仁应当属刚,不属于柔。如其晚年《答董叔重》书论此最明:
(董问)阴阳以气言,刚柔则有形质可见矣。至仁与义,则又合气与形而理具焉。然仁为阳刚,义为阴柔,仁主发生,义主收敛,故其分属如此。或谓杨子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盖取其相济而相为用之意。
(朱答)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22]
汉代的扬雄以仁为柔,以义为刚,这是讲得通的。而朱子与之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来自朱子从宇宙生化论讲四德,主张以发生论仁,以收敛论义,由于是以收敛为阴柔,所以便以发生为阳刚了。仁是发生原则,故仁属阳刚。值得注意的是,董铢在这里提出“仁义”是“合气与形而理具焉”,按这个说法,仁、义似乎不仅仅是性理,而是实存的气形统一整体或总体,其中具有理。当然,也可以说理气合而后生人,而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个说法应该是顺就朱子的说法而来,故朱子没有加以评论。
朱子曾与袁枢反复辨析阴阳刚柔之义,其《答袁机仲》书云:
凡此崎岖反复,终不可通,不若直以阳刚为仁、阴柔为义之明白而简易也。盖如此,则发生为仁、肃杀为义,三家之说皆无所牾,肃杀虽似乎刚,然实天地收敛退藏之气,自不妨其为阴柔也。
……又读来书,以为不可以仁义礼智分四时,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时之相配,其为理甚明而为说甚久,非熹独于今日创为此论也。[23]
这里朱子自己界定得很清楚,发生为刚,肃杀为柔,肃杀收敛退藏应属于阴柔,义为肃杀退藏,故当属于阴柔。故阳刚为仁,阴柔为义。
而朱子的这一说法,遭到了不少质疑,引发了朱子与这些质疑的辩难。如其《答袁机仲别幅》云:
……来喻以东南之温厚为仁、西北之严凝为义,此《乡饮酒义》之言也。然本其言虽分仁义,而无阴阳柔刚之别,但于其后复有阳气发于东方之说,则固以仁为属乎阳,而义之当属乎阴,从可推矣。来谕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为柔、以义为刚,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属乎阳、刚之不可属乎阴也,于是强以温厚为柔、严凝为刚。又移北之阴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阳以就北,而使主乎义之刚,其于方位气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为说者,率皆参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东北之为阳、西南之为阴,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于图子已具见其失矣。盖尝论之: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此阴阳之所以为柔刚也。阳刚温厚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以此观之,则阴阳刚柔仁义之位岂不晓然?而彼杨子云之所谓“于仁也柔,于义也刚”者,乃自其用处之末流言之,盖亦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固不妨自为一义,但不可以杂乎此而论之尔。[24]
袁枢并不反对仁为阳,义为阴,但反对以仁为刚,以义为柔,而主张温厚为柔,严凝为刚,故仁为柔为阳,义为刚为阴。朱子坚持仁属于阳刚,义属于阴柔,阳刚主生长,阴柔主敛藏。他认为杨雄所说的“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不是从本体上说的,而是从发用上说的,所以朱子主张“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认为这样就可以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了。朱子又说:
前书所论仁义礼智分属五行四时,此是先儒旧说,未可轻诋。今者来书虽不及之,然此大义也,或恐前书有所未尽,不可不究其说。盖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阴分阳,便是两物,故阳为仁而阴为义。然阴阳又各分而为二,故阳之初为木为春为仁,阳之盛为火为夏为礼,阴之初为金为秋为义,阴之极为水为冬为智。盖仁之恻隐方自中出,而礼之恭敬则已尽发于外,义之羞恶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则已全伏于中,故其象类如此,非是假合附会。若能默会于心,便自可见。“元亨利贞”,其理亦然。《文言》取类,尤为明白,非区区今日之臆说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属,而土居中宫,为四行之地、四时之主,在人则为信、为真实之义,而为四德之地、众善之主也。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盖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若不见得,则虽生于天地间,而不知所以为天地之理,虽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故此一义切于吾身,比前数段尤为要紧,非但小小节目而已也。[25]
照此说法,天地一气,分阴分阳,阳为仁、阴为义;阳中又分为二,即春仁和夏礼;阴中亦分为二,即秋义和冬智。一气分为阴阳,并无先后,而阳再分为二,春仁在先,夏礼在后;阴之分二亦然,秋义在先,冬智在后,这是一气流行的次序。而人性的仁义礼智之间及其发作为情,并无先后。总之,论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不能离开一气阴阳四时五行这些宇宙论要素,从而使得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也成为与一气阴阳纠缠在一起的流行实体了。
六
朱子《周易本义》论元亨利贞四德:
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26]
这是把元亨利贞四德作为“物”的发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来理解的,同时,又说明这四个连续无间段的流行,是生气流行,元就是生气,所以四者的连续流行就是体现了“元”贯通四者而作为天道的统一性。
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泳。[27]
当来即当初。以生说仁,把生作为天地间的普遍原理,这是“人生而静以上”事,即生化论属于宇宙论之事,不是人生论之事。因此宇宙论对于人生论来说是“上一节事”。人之生亦接受天地之生理,人生而静以下此生理即体于人而为仁之理,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体认从天地接受的生意生理,因为这是人的生命的根源。
《语类》卷六八论乾卦四德:
文王本说“元亨利贞”为大亨利正,夫子以为四德。梅蘂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节。[28]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而不是以元亨利贞为性。
致道问“元亨利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阴阳极处,其间春秋便是过接处。”恪。[29]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之外,又以元亨利贞对应春夏秋冬。
《乾》之四德,元,譬之则人之首也;手足之运动,则有亨底意思;利则配之胸脏;贞则元气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脏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属木,木便是元;心属火,火便是亨;肺属金,金便是利;肾属水,水便是贞。”道夫。[30]
这是以元亨利贞对木火金水。这就使元亨利贞成为更普遍的模式了。
“元亨利贞”,譬诸谷可见,谷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实是贞。谷之实又复能生,循环无穷。德明。[31]
这也是以物之生长遂成体现元亨利贞。以上都是以元亨利贞为物之形态或阶段。
以物之生长收藏说元亨利贞四德之义,始于程伊川,朱子亦明言之:
“元亨利贞”,理也;有这四段,气也。有这四段,理便在气中,两个不曾相离。若是说时,则有那未涉于气底四德,要就气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说:“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实;贞者,物之成。”这虽是就气上说,然理便在其中。伊川这说话改不得,谓是有气则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说,便可见得物里面便有这理。若要亲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恻隐须有恻隐底根子,羞恶须有羞恶底根子,这便是仁义。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说,更无说处。仁义礼智,似一个包子,里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浑然,非有先后,元亨利贞便是如此,不是说道有元之时,有亨之时。渊。[32]
有这四段,即指生长遂成四个阶段,朱子在这里以生长遂成四阶段为气,而以元亨利贞为生长遂成的现实过程所体现和依据的理。按前面所述多见以元亨利贞为气这类的说法,而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理,以生长收藏四段为气,此说似不多见。照这个说法,以生长遂成说元亨利贞,是就气上说,而理在气中。但朱子特别强调,程颐不从理上说元亨利贞,而从物上说,并没有错,他甚至声称程颐此说不可更改,认为讲气讲物,理便在其中了。此中理气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说的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的思想,不是从性、从理、从体上看,而都是近于从总体上看的方法。
“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他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渊。[33]
这里又把元亨利贞说成四阶段连接循环,元是生气发生的阶段。元之前是贞,贞之后是元,循环无间断处。
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如子时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无空阙时。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故《易传》只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不说气,只说物者,言物则气与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说四句自动不得,只为“遂”字、“成”字说不尽,故某略添字说尽。高。[34]
“局定底”与“推行底”,与朱子说《易》的方法“定位底”和“流行底”的分别相近,显然,元亨利贞是属于“流行底”道理。由于伊川论元亨利贞是指“物”之生、长、遂、成言,故朱子说元亨利贞“就物上看亦分明”,他甚至认为《易传》也是就“万物”而言四德,就万物之生长遂成的阶段言元亨利贞。这种“就物上说”的方法并没有忽视理和气,因为言物则气和理皆在其中。这似乎是说,元亨利贞四德的论法可以有三种,物上说的方法如生长遂成说,气上说的方法如春夏秋冬说,理上说的方法即元亨利贞说。这三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说明的。
朱子又说: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节。[35]
这就把元亨利贞之理更普遍化了,就天道言,即就宇宙普遍法则而言,是元亨利贞;这样普遍法则理一而分殊,有不同的体现,如在四时体现为春夏秋冬,在人道体现为仁义礼智,在气候体现为温凉燥湿,在四方体现为东南西北。温凉燥湿又说为温热凉寒:“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36]这实际上是用四季的气候变化循环说元亨利贞。在这个意义上,元亨利贞如同理一分殊,已经成为一种论述模式。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会也”,好底会聚也。义者,宜也,宜即义也;万物各得其所,义之合也。“干事”,事之骨也,犹言体物也。看此一段,须与《太极图》通看。贺孙。[37]
《文言传》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就人事道德上说,朱子具体解释了什么是善之长,什么是嘉之会,什么是义之合,什么是事之干,但朱子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并不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朱子强调,根据二程的说法,对“元”的理解要与“仁”联系一起、贯通在一起。
光祖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处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便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问:“这犹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礼是火,义是金,智是水。”贺孙。[38]
按朱子的解释,元是初发生,则这就不是从理上看,而是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其次,发生后必然向会通发展,会通后必然向成熟发展。就四个阶段的不同展开说,这是“偏言”的角度。就四个阶段贯穿着作为统一性的“元”而言,这是“专言”的角度。专言包四者,朱子的解释是,一方面,元中具亨利贞许多道理,亨利贞都是元的发现的不同形态,同理,仁不仅发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仁之发。
《语类》又载:
曾兄亦问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卓。[39]
元是生物的发端,元是生意的开始,亨是生意的长,利是生意的遂,贞是生意的成。于是生长遂成就是“生意”的生长遂成。这都不是从理上看的方法,也说明,四德的意义在朱子思想中并不仅仅是理。
《周易本义》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40]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41]
元既是生物之始,又是天地之德,作为生物之始,亦体现为四时之春;作为天地之德,亦体现为人道之仁。可见,元亨利贞四德既是论生物过程与阶段,又是论天地之德,于是既体现为四时春夏秋冬,又体现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流行之统体”就是兼体用的变易总体,元亨利贞是此一统体不同流行的阶段及其特征。
虽然可以说,对于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看,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中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就是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后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有《元亨利贞说》,文云: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2]
《元亨利贞说》写于朱子四十二岁前后,属于其前期思想。朱子当时以元亨利贞四者为性,与生长收藏相对待;这和以仁义礼智为性、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是相对应的也是一致的。元亨利贞是天地之性,天地之化以天地之性为根据,而实现生长收藏的过程。同理,仁义礼智是人之性,人心之动以人之性为根据,而发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这种分析体现了朱子当时对性情之辨的重视。在这种话语中,元亨利贞只是性,与生长收藏的现实过程被严格分别开来,生长收藏相当于情,也就是用。
不久,朱子又有《仁说》之作,其中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
依朱子这里的看法,仁是“人心”之德,元亨利贞是“天地之心”之德,这是明确把仁和元、亨、利、贞都作为“德”。就心之德作为性而言,“元”包“亨利贞”,这是从体上来看的。朱子还认为,四季运行是天地之化的过程,是用,而天地之德则是运行过程的内在根据。从天地运行的大用着眼,春生之气贯通于春夏秋冬的有序连接,无所不通。如果从人的方面看,就心之徳言,“仁”包“义礼智”;就四德的发用言,恻隐贯通于爱恭宜别四种情感。在这种论述中,春生之气相当于恻隐,都属用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运行、流行是就“用”言,而仁义礼智或元亨利贞是“体”,是“性”,是无所谓流行的。既然性无所谓流行,这说明前期朱子思想在性情体用之辨的意识主导下,不采用“流行”一类的观念解释四德。我们在前文已说明,以“流行”的观念解释四德关系,见于朱子后期思想,而“运用流行”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和气的哲学思维分不开的。从哲学上看,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性和情两者的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总体的了解,这就是所谓“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心不是本性、体,也不是过程、用,而是包涵体用的、存在与活动的总体。
二
《文集》卷七四有《玉山讲义》,是朱子晚年六十五岁经过江西玉山时所作,其中论述了四德说。此讲义可分为三部分,其第一部分云:
时有程珙起而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4]
程珙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孔子只说仁,不说仁义,因为孔子说仁是讲元气;而孟子说仁义,是讲阴阳二气。这个讲法其实合于朱子晚年以仁为生气流行贯通四者的思想。程珙还把仁义的关系理解为体用的关系。朱子认为他讲的不分明,强调“仁义”二字的前提先要从人性论上去理解。天赋予每个所生之物一个道理,人身得到的这个道理便是性,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以这五种都是人性的道理。就五者都是人性的内容而言,彼此并无体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仁是体、义是用。
其第二部分云:
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5]
“仁是温和慈爱的道理”,道理即理,道理之在我者即性,说明这里是把“仁”作为理看待的。所谓温和慈爱的道理,与《四书章句集注》所说“仁者爱之理”[6]的意思相通,也就是说,“仁”是发为慈爱的内在根据。慈爱是已发而为用的,属于发见的层次;仁则是体,是未发的层次。义、礼、智皆然。仁义礼智之间的分别,亦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发见不同,仁发为慈爱,义发为断制,礼发为恭敬,智发为是非。“仁”是发为慈爱的根据道理,“义”是发为断制的根据道理,“礼”是发为恭敬的根据道理,“智”是发为是非的根据道理。但朱子晚年并不简单直截地说仁是恻隐之理,义是羞恶之理,礼是恭敬之理,智是是非之理,而常常说“仁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截割底道理”等,表示朱子的这种“道理”的表述还是有其特殊意义,这就是,朱子这时已经常常用“意思说”来表达其四德说了(详见前文)。此外,在这种说法中,朱子所体现的态度是即用明体、即用论体、不可离用说体,这与体用分析的说法有别。
第三部分云:
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着,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功夫处矣。”[7]
这里就用了“意思说”,强调仁是生的意思,即仁作为“生意”的思想。朱子认为仁之生意通贯周流于仁义礼智四者之中,初看起来,仁之生意贯通的讲法似是指仁的普遍性,而以四者为特殊性;其实这种“通贯周流”的讲法与普遍性体现为特殊性的思维还是有所不同的,要言之,“通贯周流”是气论的表达方式。分别而言,仁是仁之生意的本体的表现,义是仁之生意表现为断制的阶段,礼是仁之生意的节文,智是仁之生意表现为分别。朱子认为,这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之中一样,朱子用这种周流贯通之气的流行论,发挥了程颢的生意说与程颐仁“包”四德的观念,使得“仁”也成为或具有流行贯通能力的实体。这样的仁,既不是内在的性体,又不是外发的用,而是兼体用而言的了。气论的思维在这里也明显发生作用。这些就与前期的思想有所不同了。朱子的这一思想与程珙所提的“仁是元气”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元气不如生气说得更清楚,“元气”必须落在“生”字上讲,这是二程到朱子的仁说所一直强调的。关于礼是仁之著,智是义之藏的说法,以及仁义的体用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结合《语类》再予讨论。
由此可见,《玉山讲义》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一个是四德与四端的未发已发说,一个是仁之生意流行于四德说。在稍后答陈器之书中,朱子复述了这两点,并对“对立成两”、“仁智终始”等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
三
《文集》卷五八载《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该信可分为四节,其开首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
四
《文集》卷六七有《周礼三德说》,该文虽然不是讨论四德之说,但其中讨论周礼三德说涉及的对德、行的理解也值得注意。文之开首云:
或问:师氏之官,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何也?曰:至德云者,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则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行”则理之所当为,日可见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恶,则以得于己者笃实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恶,而自不忍为者也。(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则赵无愧、徐仲车之徒是已。)凡此三者,虽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见其相须为用而不可偏废之意。盖不知至德,则敏德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则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陈备举而无所遗,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资、精粗两尽而不倚于一偏也。[13]
“三德”、“三行”之说出于《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4]这是古代德行论的早期表达。
朱子对三德、三行作了明确的哲学的、伦理学的解说。在朱子看来,以三种德行教国子,至德是指心而言,是关于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所谓至德以为道本,是说至德是掌握性命之理、践行当然之则、实行治国平天下之术的根本与基础,突出了德性对哲学理解、道德实践、政治施行的根本意义,强调心徳是道术的根本基础。强志力行,即《礼记·儒行》第一条所说的强学力行;一切行为都是由心志而发,人能强化心志,力行理所当为,使心志在行为事迹上表现出来,这是敏德。所谓敏德以为行本,是指由心志落实到行为是德行的一般特性。照朱子的这个说法,从德行论来看,可以说正心诚意是根本的德行,称为至德;强志力行是一般意义的德行,称为敏德;尊祖爱亲是专指孝的特殊德行,称为孝德。三徳可以说区别了根本德行、一般德行、特殊德行。
以三德教国子,说明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成人。但把国子培养为成人,必须使他们同时培养三德,不可偏专其中之一。朱子认为三德互相补充、互相需要,“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也就是说三德具有统一性。没有至德,敏德只能笃行,而没有方向,不能知“道”;没有敏德,至德就会流于空洞,无法具体落实,也无法拓宽事业;不落实到孝德,敏德就失去基础。至德是方向,敏德是分殊,孝德是基础。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盖不本之以其德,则无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实之以其行,则无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进。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继之,则虽其至末至粗亦无不尽,而德之修也不自觉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则无与焉。盖二者之行,本无常师,必协于一,然后有以独见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预言也。唯孝德则其事为可指,故又推其类而兼为友顺之目以详教之,以为学者虽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则进乎德而无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溯其原,则孰谓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乡三物之为教也亦然,而已详。[15]
三德之教和三行之教,涉及对德与行的分别。在对教三行的解释上,朱子解释了什么是德、行,他说“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这是说,“德”是得于心的状态或性质,“行”是对规范的实行。朱子认为,德和行互相支持、互相连接,不以内心之德为本,就达不到自得,行为也不能自修;心之德不落实在行为表现出来,心难以持循,心德也不能进步。朱子也指出,人有时未得于心,但能勉而行之,在这种状态下不能说德在心中。但如此勉而行之,久而久之,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不断实行便可使人达到“得于心”,即促使德在心中形成,这时的行为便是从心中之德出发,不待勉强了。这是朱子对德性形成的一种看法。
朱子还说过:
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泳。[16]
聪、明是耳目的根本属性,仁是心的根本属性,德即指根本属性而言。
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节。[17]
百行是行为,仁义礼智是本性,这是强调一切行为都是发自于内在的本性,也体现了朱子德性论强调性理的特色。
五
《周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8]此后,儒学思想家常常依此思路,努力把仁义与阴阳、刚柔对应起来,以建立宇宙论的统一性说明。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僴。[19]
理学倾向于把“阴阳”作为普遍的哲学分析方法。按照这种分析,如果把仁义礼智四者归为阴阳两类,那么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何者为阳,何者为阴?朱子的主张是,仁和礼属于阳,义和智属于阴。在他看来,以流行的次序而言,是仁、礼、义、智,也就是仁相当于春,礼相当于夏,义相当于秋,智相当于冬。因此若要把四德分为阴阳的话,仁、礼为阳,义、智为阴;正如要把一年四季分为阴阳的话,以春夏为阳,以秋冬为阴。反过来说,如果把四季分为仁义二者,则以春夏为仁,以秋冬为义。这种思维是汉代以来阴阳气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不过,这样一来,仁、礼、义、智的次序便和习惯所用的仁、义、礼、智的顺序有所不同了,朱子回答学生的疑问:
问:“孟子说仁义礼智,义在第二;《太极图》以义配利,则在第三。”曰:“礼是阳,故曰亨。仁义礼智,犹言东西南北;元亨利贞,犹言东南西北。一个是对说,一个是从一边说起。”夔孙。[20]
按朱子的理解,如同一个圆圈,顺着圆圈的次序是流行的次序,即仁、礼、义、智的排序。以流行言,仁对应元,礼对应亨,义对应利,智对应贞。如果不顺着圆圈,而以南北相对,东西相对,这样的次序就不是流行的次序,而是对待的次序,这就是仁、义、礼、智的排序。
问:“‘元亨利贞’,《乾》之四德;仁义礼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礼,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礼义智,犹言春夏秋冬也;仁义礼智,犹言春秋夏冬也。”铢。[21]
这也是说明四德有两种排序。仁、礼、义、智的顺序是合乎元气流行的自然次序,这样的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是被用气的流行来刻划的东西了,也就成为他所说的“流行之统体”了。
中国哲学中与“阴阳”分析相配合的是“刚柔”的分析。按上面的说法,仁属于阳,义属于阴,那么仁义与刚柔又如何对应呢?在一般人看来,仁有柔软的意思,应当属柔,不应当属刚,而朱子却认为仁应当属刚,不属于柔。如其晚年《答董叔重》书论此最明:
(董问)阴阳以气言,刚柔则有形质可见矣。至仁与义,则又合气与形而理具焉。然仁为阳刚,义为阴柔,仁主发生,义主收敛,故其分属如此。或谓杨子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盖取其相济而相为用之意。
(朱答)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22]
汉代的扬雄以仁为柔,以义为刚,这是讲得通的。而朱子与之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来自朱子从宇宙生化论讲四德,主张以发生论仁,以收敛论义,由于是以收敛为阴柔,所以便以发生为阳刚了。仁是发生原则,故仁属阳刚。值得注意的是,董铢在这里提出“仁义”是“合气与形而理具焉”,按这个说法,仁、义似乎不仅仅是性理,而是实存的气形统一整体或总体,其中具有理。当然,也可以说理气合而后生人,而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个说法应该是顺就朱子的说法而来,故朱子没有加以评论。
朱子曾与袁枢反复辨析阴阳刚柔之义,其《答袁机仲》书云:
凡此崎岖反复,终不可通,不若直以阳刚为仁、阴柔为义之明白而简易也。盖如此,则发生为仁、肃杀为义,三家之说皆无所牾,肃杀虽似乎刚,然实天地收敛退藏之气,自不妨其为阴柔也。
……又读来书,以为不可以仁义礼智分四时,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时之相配,其为理甚明而为说甚久,非熹独于今日创为此论也。[23]
这里朱子自己界定得很清楚,发生为刚,肃杀为柔,肃杀收敛退藏应属于阴柔,义为肃杀退藏,故当属于阴柔。故阳刚为仁,阴柔为义。
而朱子的这一说法,遭到了不少质疑,引发了朱子与这些质疑的辩难。如其《答袁机仲别幅》云:
……来喻以东南之温厚为仁、西北之严凝为义,此《乡饮酒义》之言也。然本其言虽分仁义,而无阴阳柔刚之别,但于其后复有阳气发于东方之说,则固以仁为属乎阳,而义之当属乎阴,从可推矣。来谕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为柔、以义为刚,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属乎阳、刚之不可属乎阴也,于是强以温厚为柔、严凝为刚。又移北之阴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阳以就北,而使主乎义之刚,其于方位气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为说者,率皆参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东北之为阳、西南之为阴,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于图子已具见其失矣。盖尝论之: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此阴阳之所以为柔刚也。阳刚温厚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以此观之,则阴阳刚柔仁义之位岂不晓然?而彼杨子云之所谓“于仁也柔,于义也刚”者,乃自其用处之末流言之,盖亦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固不妨自为一义,但不可以杂乎此而论之尔。[24]
袁枢并不反对仁为阳,义为阴,但反对以仁为刚,以义为柔,而主张温厚为柔,严凝为刚,故仁为柔为阳,义为刚为阴。朱子坚持仁属于阳刚,义属于阴柔,阳刚主生长,阴柔主敛藏。他认为杨雄所说的“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不是从本体上说的,而是从发用上说的,所以朱子主张“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认为这样就可以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了。朱子又说:
前书所论仁义礼智分属五行四时,此是先儒旧说,未可轻诋。今者来书虽不及之,然此大义也,或恐前书有所未尽,不可不究其说。盖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阴分阳,便是两物,故阳为仁而阴为义。然阴阳又各分而为二,故阳之初为木为春为仁,阳之盛为火为夏为礼,阴之初为金为秋为义,阴之极为水为冬为智。盖仁之恻隐方自中出,而礼之恭敬则已尽发于外,义之羞恶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则已全伏于中,故其象类如此,非是假合附会。若能默会于心,便自可见。“元亨利贞”,其理亦然。《文言》取类,尤为明白,非区区今日之臆说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属,而土居中宫,为四行之地、四时之主,在人则为信、为真实之义,而为四德之地、众善之主也。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盖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若不见得,则虽生于天地间,而不知所以为天地之理,虽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故此一义切于吾身,比前数段尤为要紧,非但小小节目而已也。[25]
照此说法,天地一气,分阴分阳,阳为仁、阴为义;阳中又分为二,即春仁和夏礼;阴中亦分为二,即秋义和冬智。一气分为阴阳,并无先后,而阳再分为二,春仁在先,夏礼在后;阴之分二亦然,秋义在先,冬智在后,这是一气流行的次序。而人性的仁义礼智之间及其发作为情,并无先后。总之,论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不能离开一气阴阳四时五行这些宇宙论要素,从而使得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也成为与一气阴阳纠缠在一起的流行实体了。
六
朱子《周易本义》论元亨利贞四德:
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26]
这是把元亨利贞四德作为“物”的发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来理解的,同时,又说明这四个连续无间段的流行,是生气流行,元就是生气,所以四者的连续流行就是体现了“元”贯通四者而作为天道的统一性。
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泳。[27]
当来即当初。以生说仁,把生作为天地间的普遍原理,这是“人生而静以上”事,即生化论属于宇宙论之事,不是人生论之事。因此宇宙论对于人生论来说是“上一节事”。人之生亦接受天地之生理,人生而静以下此生理即体于人而为仁之理,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体认从天地接受的生意生理,因为这是人的生命的根源。
《语类》卷六八论乾卦四德:
文王本说“元亨利贞”为大亨利正,夫子以为四德。梅蘂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节。[28]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而不是以元亨利贞为性。
致道问“元亨利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阴阳极处,其间春秋便是过接处。”恪。[29]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之外,又以元亨利贞对应春夏秋冬。
《乾》之四德,元,譬之则人之首也;手足之运动,则有亨底意思;利则配之胸脏;贞则元气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脏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属木,木便是元;心属火,火便是亨;肺属金,金便是利;肾属水,水便是贞。”道夫。[30]
这是以元亨利贞对木火金水。这就使元亨利贞成为更普遍的模式了。
“元亨利贞”,譬诸谷可见,谷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实是贞。谷之实又复能生,循环无穷。德明。[31]
这也是以物之生长遂成体现元亨利贞。以上都是以元亨利贞为物之形态或阶段。
以物之生长收藏说元亨利贞四德之义,始于程伊川,朱子亦明言之:
“元亨利贞”,理也;有这四段,气也。有这四段,理便在气中,两个不曾相离。若是说时,则有那未涉于气底四德,要就气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说:“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实;贞者,物之成。”这虽是就气上说,然理便在其中。伊川这说话改不得,谓是有气则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说,便可见得物里面便有这理。若要亲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恻隐须有恻隐底根子,羞恶须有羞恶底根子,这便是仁义。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说,更无说处。仁义礼智,似一个包子,里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浑然,非有先后,元亨利贞便是如此,不是说道有元之时,有亨之时。渊。[32]
有这四段,即指生长遂成四个阶段,朱子在这里以生长遂成四阶段为气,而以元亨利贞为生长遂成的现实过程所体现和依据的理。按前面所述多见以元亨利贞为气这类的说法,而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理,以生长收藏四段为气,此说似不多见。照这个说法,以生长遂成说元亨利贞,是就气上说,而理在气中。但朱子特别强调,程颐不从理上说元亨利贞,而从物上说,并没有错,他甚至声称程颐此说不可更改,认为讲气讲物,理便在其中了。此中理气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说的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的思想,不是从性、从理、从体上看,而都是近于从总体上看的方法。
“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他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渊。[33]
这里又把元亨利贞说成四阶段连接循环,元是生气发生的阶段。元之前是贞,贞之后是元,循环无间断处。
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如子时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无空阙时。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故《易传》只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不说气,只说物者,言物则气与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说四句自动不得,只为“遂”字、“成”字说不尽,故某略添字说尽。高。[34]
“局定底”与“推行底”,与朱子说《易》的方法“定位底”和“流行底”的分别相近,显然,元亨利贞是属于“流行底”道理。由于伊川论元亨利贞是指“物”之生、长、遂、成言,故朱子说元亨利贞“就物上看亦分明”,他甚至认为《易传》也是就“万物”而言四德,就万物之生长遂成的阶段言元亨利贞。这种“就物上说”的方法并没有忽视理和气,因为言物则气和理皆在其中。这似乎是说,元亨利贞四德的论法可以有三种,物上说的方法如生长遂成说,气上说的方法如春夏秋冬说,理上说的方法即元亨利贞说。这三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说明的。
朱子又说: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节。[35]
这就把元亨利贞之理更普遍化了,就天道言,即就宇宙普遍法则而言,是元亨利贞;这样普遍法则理一而分殊,有不同的体现,如在四时体现为春夏秋冬,在人道体现为仁义礼智,在气候体现为温凉燥湿,在四方体现为东南西北。温凉燥湿又说为温热凉寒:“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36]这实际上是用四季的气候变化循环说元亨利贞。在这个意义上,元亨利贞如同理一分殊,已经成为一种论述模式。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会也”,好底会聚也。义者,宜也,宜即义也;万物各得其所,义之合也。“干事”,事之骨也,犹言体物也。看此一段,须与《太极图》通看。贺孙。[37]
《文言传》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就人事道德上说,朱子具体解释了什么是善之长,什么是嘉之会,什么是义之合,什么是事之干,但朱子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并不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朱子强调,根据二程的说法,对“元”的理解要与“仁”联系一起、贯通在一起。
光祖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处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便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问:“这犹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礼是火,义是金,智是水。”贺孙。[38]
按朱子的解释,元是初发生,则这就不是从理上看,而是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其次,发生后必然向会通发展,会通后必然向成熟发展。就四个阶段的不同展开说,这是“偏言”的角度。就四个阶段贯穿着作为统一性的“元”而言,这是“专言”的角度。专言包四者,朱子的解释是,一方面,元中具亨利贞许多道理,亨利贞都是元的发现的不同形态,同理,仁不仅发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仁之发。
《语类》又载:
曾兄亦问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卓。[39]
元是生物的发端,元是生意的开始,亨是生意的长,利是生意的遂,贞是生意的成。于是生长遂成就是“生意”的生长遂成。这都不是从理上看的方法,也说明,四德的意义在朱子思想中并不仅仅是理。
《周易本义》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40]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41]
元既是生物之始,又是天地之德,作为生物之始,亦体现为四时之春;作为天地之德,亦体现为人道之仁。可见,元亨利贞四德既是论生物过程与阶段,又是论天地之德,于是既体现为四时春夏秋冬,又体现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流行之统体”就是兼体用的变易总体,元亨利贞是此一统体不同流行的阶段及其特征。
虽然可以说,对于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看,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中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就是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后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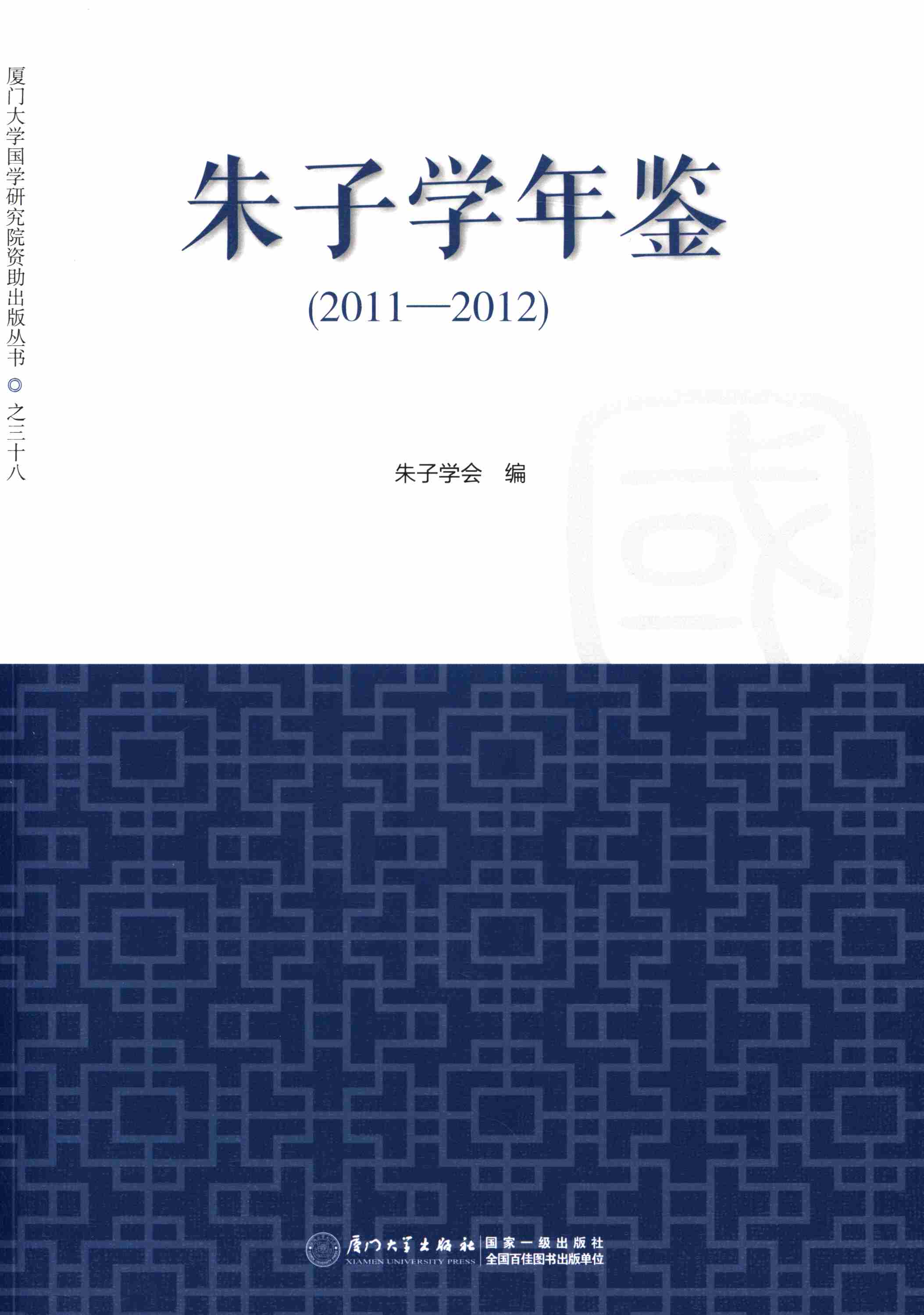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2011-2012年朱子学年鉴。内容包括本刊特稿2篇、朱子学研究新视野7篇、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6篇、朱子学研究新著38篇、朱子学书评3篇、朱子学研究优秀硕博士论文82篇、朱子学研究论文荟萃54篇、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4篇、朱子学国内外学术动态6篇、朱子学研究机构介绍3篇、朱子学研究学者介绍13篇、2011-2012年朱子学新书索引、2011-2012年朱子学论文索引556篇等。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来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