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气流行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367 |
| 颗粒名称: | 四、生气流行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31-3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四德论中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四德(仁、义、礼、智)与天地间的一气流行相对应,认为它们都是生气的表现。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在分别考察时各是道德概念,但从整体来看,它们都是仁的表现,在不同阶段展现出来。他认为仁是生意的流行,而生意又是生生不息的倾向。仁与一元之气的流行结构相似,都通过循环发展形成不同阶段。朱子还指出,仁是生气,它包含义、礼、智,整体而言,仁是天地之生气,仁义礼智只是在其中分别展现而已。 |
| 关键词: | 朱子四德论 生气流行 一元之气 |
内容
朱子四德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四德:
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一个。”淳[20]
这是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这个一气流行又称一元之气。一元之气就是从整体上看,不分别阴阳二气。一气是流行反复的:“流行”即不断运行,“反复”是说流行是有阶段的、反复的,如一年四季不断流行反复。四季分开来看,每个不同;连接起来看,则只是一元之气流行的不同阶段。朱子认为,仁义礼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所以,朱子又说:“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淳。”[21]就分别来说,与义礼智相区别的“仁”是生意,“生意”即生生不息之倾向;而就整体来说,仁义礼智都是仁的表现,都是生生之意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表现。
“仁有两般:有作为底,有自然底。看来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为。……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著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著义,便有礼智相对。以一岁言之,便有寒暑;以气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阴阳之间,尽有次第。大寒后,不成便热,须是且做个春温,渐次到热田地。大热后,不成便寒,须是且做个秋叙,渐次到寒田地。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穀种、桃仁、杏仁之类,种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渐渐收敛,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进去,秋冬是退后去。正如人呵气,呵出时便热,吸入时便冷。”明作。[22]
仁是生意,有流行。“元只是一物”,这里指仁;“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指仁义礼智。朱子认为天地间事物都是如此,一元流行,而自然形成几个次第界限,如气之流行便成春夏秋冬,木之流行便成金木水火土,循环往复。冬至一阳来复,生意又复发起,生长收藏,不断循环。仁之流行,循着四个阶段往复不断,不管仁的流行所形成的仁义礼智四阶段与生物流行自然成春夏秋冬四季如何对应一致,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静而不动的理、性了。
那么,仁是生意,仁是不是生气呢?上面引用的陈淳录的材料只是把仁义礼智与一元之气的流行加以类比,认为仁相当于一元生气,两者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还没有说明仁是生气。
下面的材料则更进了一步。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可学。[23]
分别来看,春是生气,冬是肃杀之气,但春夏秋冬,只是一气流行的不同阶段;以冬之肃杀而言,冬季的肃杀之气并不是与春季开始的生气不同的另一种气,只是生气运行到此阶段,有所收敛。照这里的答问来看,朱子不仅认为仁是生意,也肯定仁是生气;不仅仁是生气,仁义礼智全体也是生气。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也采用二程“专言之则包四者”的说法,说仁包义礼智(信),只是他已赋予仁包四者以生气流行的意义。从理论上来分析,如果仁是生气流行,这个仁就不能是理,不能是性,而近于生气流行的总体了。在心性论上,这样的仁就接近于心体流行的总体了。只是,朱子并没有把这一思想彻底贯彻到心性论。
《朱子语类》又载:
蜚卿问:“仁包得四者,谓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道夫问:“向闻先生语学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此难说,若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后,但其灌注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24]
这也是用酿酒的过程和一日早晚的过程,来类比说明四德是流行的不同阶段。这样一来,仁义礼智四德不再只是道德的德目,而变为与元亨利贞四德一样,也是自然之德,仁义礼智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德也自然化了,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的同一,导致自然与社会节度的混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灌注”即流住、流行,指五行之气自相灌注,灌注的次序便是五行展开的次序。朱子这里所说,也意味着仁义礼智四德与五行之气一样,是按一定的灌注次序展开的。只是,这里四德展开的次序是仁礼义智,而不是仁义礼智,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把仁义礼智四德类比于五行之气的流行灌注,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显示出气的思维对朱子四德论的影响。
当然,在朱子的论述中,酿酒和一日早晚的例子,不如一年四季变化更为常用:
只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四者于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25]
这样来看,自然流行的节度,总是生、长、遂、成,不断循环往复;与生、长、遂、成四个阶段相对应,便是元、亨、利、贞四德,四德分别是生、长、遂、成各自阶段的性质、属性、性向,也可以说是每个阶段的德性。照朱子看来,与生、长、遂、成相对应的属性、德性,既可以说是元、亨、利、贞,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这两个说法是一致的。这无异于说,仁义礼智在这里是自然属性的范畴。这就把仁义礼智自然化、宇宙论化了,这样的仁义礼智就不仅有道德的意义,也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要强调的是,当朱子把仁义礼智作为自然化的范畴时,绝不表示作为自然化了的仁义礼智与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概念已经根本不同,已经是两回事;不,在朱子哲学,自然化的仁义礼智与人道的仁义礼智仍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是用法与意义有广有狭而已。
所以,朱子更断言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泳。”[26]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这在无形之中使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
《朱子语类》:“问:‘元亨利贞有次第;仁义礼智因发而感,则无次第。’曰:‘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佐。”[27]“发时无次第”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感发生是没有一定次序的,“生时有次第”是指仁义礼智作为生气流行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按学生的提问,元亨利贞的次序即春夏秋冬的流行次序,是实际流行的次第,而仁义礼智都是由感而发,不一定有固定的次序。这样,二者不就是不一致了吗?学生所说的仁义礼智还是局限于性情的仁义礼智,而朱子所说的流行的仁义礼智已不限于性情之发,“生时有次第”就是指作为生气流行的仁义礼智有其次序。这些都再次体现了四德具有生气流行的意义。当然,在最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生时有次第”包含着仁义礼智四者在逻辑上的次序。
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接续处。[28]
说“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即是把仁义礼智看作流行的事物,而流行是一个过程,一个渐渐起伏变化的过程;这一无尽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断延伸的单元所组成,每个单元都由开始、中间、结束构成内部三个阶段,或由生、长、遂、成构成内部四个阶段。一方面,每个单元的后续阶段都是由开始阶段渐渐衍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每个单元中开始的阶段和终结的阶段更为重要。
味道问:“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逊、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而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时举。[29]
元是生气,元包亨利贞;仁是生意,仁包义礼智;木是生气,木包火金水。于是四德、五常、五行三者被看成是同一生气流行的不同截面而已。至于五常中的信、五行中的土,在这种看法中都被消解了实体意义,而起保障其他四者为实存的作用。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朱子说: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曰:“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说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者,乃众善之长也;亨者,乃嘉之会也。嘉会,犹言一齐好也。会,犹齐也,言万物至此通畅茂盛,一齐皆好也。利者,义之和处也;贞者,乃事之桢干也。‘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体,犹所谓‘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嘉会者,嘉其所会也。一一以礼文节之,使之无不中节,乃嘉其所会也。‘利物足以和义’,义者,事之宜也;利物,则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转,‘义’字愈明白,不利物则非义矣。贞固以贞为骨子,则坚定不可移易。”铢。[30]
与中年的仁说不同,后期朱子更强调对仁的理解要合义礼智三者一起看,而这种四德兼看的方法要求与四季的看法相参照。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但夏秋冬都出于春起的生意,四季都是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即生、长、成、藏。本来,元亨利贞是生长收藏的性,不就是生长收藏的过程,而在这里,仁义礼智不像是性,而成了流行总体和过程本身。与四季类似,仁是仁的本体,礼是仁的节文,义是仁的断制,知是仁的分别,四德都出于仁,是仁的由始至终的不同阶段。于是,仁义礼智作为人事之当然,与元亨利贞作为天德之自然,成为完全同构的东西。虽然朱子并没有说人事四德即来源于自然天德,但他把这些都看成天地之化的法则或机轴。虽然生意流行与生气流行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但整体上看,两种说法应是一致的。
朱子下面的话讲得很有意味:
“今日要识得仁之意思是如何。圣贤说仁处最多,那边如彼说,这边如此说,文义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将圣贤星散说体看,处处皆是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才有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干燥。……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孔门弟子所问,都只是问做工夫。若是仁之体段意思,也各各自理会得了。今却是这个未曾理会得,如何说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31]
朱子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气观仁,从气识仁,这种观、识是要把握仁的“意思”,而仁的意思就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朱子强调,这一浑然温和之气并非仅仅是仁的道德气息,而是指出此气就是天地阳春之气。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也并非只是纯粹从气观仁,也同时从理观仁,故说了“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后,即说“其理便是天地生物之心”。浑然温和之气之中有理,此理即天地生物之心。人的存在本来是理气合一、浑然流行的,而现实的人必须自觉地在自己身上体现这种浑然流行,培养此种德性。如果在自家身上能体现这种仁的意思,使这个意思遍润己身,这个意思便能无间隔地流行于人己人物之间。如叶贺孙和赵致道所言,温和之气可以见仁,而温和之气的流行(流注)自然有节文(礼),自然得宜(义),自然明辨(智)。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如知福州是这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不是两人也。故明道谓:‘义礼智,皆仁也。若见得此理,则圣人言仁处,或就人上说,或就事上说,皆是这一个道理。’正叔云:‘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气象。《论语》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门人必尝理会得此一个道理。今但问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随其人而告之。……南升。(疑与上条同闻。)[32]
照这里所说,天地生发之理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就天地之生气来看,元亨利贞是气,是可见的;更容易看的是四季,春夏秋冬便是气的流行。在这里,四季的四个阶段的更换不是最重要的,四季中贯通的生育之气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气便是仁。这里所说的“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显然是指人的身心而言:朱子认为,这种人在私欲尽去后达到的温和之气,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气,这是以人合天的状态。这些都体现了朱子以温和之气为仁的思想。
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仁义礼智四德不仅仅是性理,在不同的讨论中,四德也具有其他的意义,如与存于中不同的心德说,如意思说所表达的道德信息说,如宇宙论意义的生气流行说,等。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就人心性命而言,仁既是性,也是心。虽然仁的这几层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互相否定的,而是可以共存的。
总之,上述仁论与四德论的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朱子的这些思想,使我们得以了解朱子不仅发挥继承了伊川的理学思想,也与明道的仁学思想有其内在的联系。对朱子仁学的思想,以往整体研究不够,需要更深入地分疏和诠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一是理学,一是仁学。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是我们以往关注的主体;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
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一个。”淳[20]
这是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这个一气流行又称一元之气。一元之气就是从整体上看,不分别阴阳二气。一气是流行反复的:“流行”即不断运行,“反复”是说流行是有阶段的、反复的,如一年四季不断流行反复。四季分开来看,每个不同;连接起来看,则只是一元之气流行的不同阶段。朱子认为,仁义礼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所以,朱子又说:“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淳。”[21]就分别来说,与义礼智相区别的“仁”是生意,“生意”即生生不息之倾向;而就整体来说,仁义礼智都是仁的表现,都是生生之意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表现。
“仁有两般:有作为底,有自然底。看来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为。……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著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著义,便有礼智相对。以一岁言之,便有寒暑;以气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阴阳之间,尽有次第。大寒后,不成便热,须是且做个春温,渐次到热田地。大热后,不成便寒,须是且做个秋叙,渐次到寒田地。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穀种、桃仁、杏仁之类,种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渐渐收敛,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进去,秋冬是退后去。正如人呵气,呵出时便热,吸入时便冷。”明作。[22]
仁是生意,有流行。“元只是一物”,这里指仁;“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指仁义礼智。朱子认为天地间事物都是如此,一元流行,而自然形成几个次第界限,如气之流行便成春夏秋冬,木之流行便成金木水火土,循环往复。冬至一阳来复,生意又复发起,生长收藏,不断循环。仁之流行,循着四个阶段往复不断,不管仁的流行所形成的仁义礼智四阶段与生物流行自然成春夏秋冬四季如何对应一致,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静而不动的理、性了。
那么,仁是生意,仁是不是生气呢?上面引用的陈淳录的材料只是把仁义礼智与一元之气的流行加以类比,认为仁相当于一元生气,两者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还没有说明仁是生气。
下面的材料则更进了一步。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可学。[23]
分别来看,春是生气,冬是肃杀之气,但春夏秋冬,只是一气流行的不同阶段;以冬之肃杀而言,冬季的肃杀之气并不是与春季开始的生气不同的另一种气,只是生气运行到此阶段,有所收敛。照这里的答问来看,朱子不仅认为仁是生意,也肯定仁是生气;不仅仁是生气,仁义礼智全体也是生气。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也采用二程“专言之则包四者”的说法,说仁包义礼智(信),只是他已赋予仁包四者以生气流行的意义。从理论上来分析,如果仁是生气流行,这个仁就不能是理,不能是性,而近于生气流行的总体了。在心性论上,这样的仁就接近于心体流行的总体了。只是,朱子并没有把这一思想彻底贯彻到心性论。
《朱子语类》又载:
蜚卿问:“仁包得四者,谓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道夫问:“向闻先生语学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此难说,若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后,但其灌注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24]
这也是用酿酒的过程和一日早晚的过程,来类比说明四德是流行的不同阶段。这样一来,仁义礼智四德不再只是道德的德目,而变为与元亨利贞四德一样,也是自然之德,仁义礼智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德也自然化了,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的同一,导致自然与社会节度的混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灌注”即流住、流行,指五行之气自相灌注,灌注的次序便是五行展开的次序。朱子这里所说,也意味着仁义礼智四德与五行之气一样,是按一定的灌注次序展开的。只是,这里四德展开的次序是仁礼义智,而不是仁义礼智,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把仁义礼智四德类比于五行之气的流行灌注,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显示出气的思维对朱子四德论的影响。
当然,在朱子的论述中,酿酒和一日早晚的例子,不如一年四季变化更为常用:
只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四者于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25]
这样来看,自然流行的节度,总是生、长、遂、成,不断循环往复;与生、长、遂、成四个阶段相对应,便是元、亨、利、贞四德,四德分别是生、长、遂、成各自阶段的性质、属性、性向,也可以说是每个阶段的德性。照朱子看来,与生、长、遂、成相对应的属性、德性,既可以说是元、亨、利、贞,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这两个说法是一致的。这无异于说,仁义礼智在这里是自然属性的范畴。这就把仁义礼智自然化、宇宙论化了,这样的仁义礼智就不仅有道德的意义,也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要强调的是,当朱子把仁义礼智作为自然化的范畴时,绝不表示作为自然化了的仁义礼智与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概念已经根本不同,已经是两回事;不,在朱子哲学,自然化的仁义礼智与人道的仁义礼智仍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是用法与意义有广有狭而已。
所以,朱子更断言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泳。”[26]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这在无形之中使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
《朱子语类》:“问:‘元亨利贞有次第;仁义礼智因发而感,则无次第。’曰:‘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佐。”[27]“发时无次第”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感发生是没有一定次序的,“生时有次第”是指仁义礼智作为生气流行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按学生的提问,元亨利贞的次序即春夏秋冬的流行次序,是实际流行的次第,而仁义礼智都是由感而发,不一定有固定的次序。这样,二者不就是不一致了吗?学生所说的仁义礼智还是局限于性情的仁义礼智,而朱子所说的流行的仁义礼智已不限于性情之发,“生时有次第”就是指作为生气流行的仁义礼智有其次序。这些都再次体现了四德具有生气流行的意义。当然,在最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生时有次第”包含着仁义礼智四者在逻辑上的次序。
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接续处。[28]
说“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即是把仁义礼智看作流行的事物,而流行是一个过程,一个渐渐起伏变化的过程;这一无尽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断延伸的单元所组成,每个单元都由开始、中间、结束构成内部三个阶段,或由生、长、遂、成构成内部四个阶段。一方面,每个单元的后续阶段都是由开始阶段渐渐衍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每个单元中开始的阶段和终结的阶段更为重要。
味道问:“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逊、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而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时举。[29]
元是生气,元包亨利贞;仁是生意,仁包义礼智;木是生气,木包火金水。于是四德、五常、五行三者被看成是同一生气流行的不同截面而已。至于五常中的信、五行中的土,在这种看法中都被消解了实体意义,而起保障其他四者为实存的作用。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朱子说: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曰:“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说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者,乃众善之长也;亨者,乃嘉之会也。嘉会,犹言一齐好也。会,犹齐也,言万物至此通畅茂盛,一齐皆好也。利者,义之和处也;贞者,乃事之桢干也。‘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体,犹所谓‘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嘉会者,嘉其所会也。一一以礼文节之,使之无不中节,乃嘉其所会也。‘利物足以和义’,义者,事之宜也;利物,则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转,‘义’字愈明白,不利物则非义矣。贞固以贞为骨子,则坚定不可移易。”铢。[30]
与中年的仁说不同,后期朱子更强调对仁的理解要合义礼智三者一起看,而这种四德兼看的方法要求与四季的看法相参照。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但夏秋冬都出于春起的生意,四季都是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即生、长、成、藏。本来,元亨利贞是生长收藏的性,不就是生长收藏的过程,而在这里,仁义礼智不像是性,而成了流行总体和过程本身。与四季类似,仁是仁的本体,礼是仁的节文,义是仁的断制,知是仁的分别,四德都出于仁,是仁的由始至终的不同阶段。于是,仁义礼智作为人事之当然,与元亨利贞作为天德之自然,成为完全同构的东西。虽然朱子并没有说人事四德即来源于自然天德,但他把这些都看成天地之化的法则或机轴。虽然生意流行与生气流行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但整体上看,两种说法应是一致的。
朱子下面的话讲得很有意味:
“今日要识得仁之意思是如何。圣贤说仁处最多,那边如彼说,这边如此说,文义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将圣贤星散说体看,处处皆是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才有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干燥。……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孔门弟子所问,都只是问做工夫。若是仁之体段意思,也各各自理会得了。今却是这个未曾理会得,如何说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31]
朱子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气观仁,从气识仁,这种观、识是要把握仁的“意思”,而仁的意思就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朱子强调,这一浑然温和之气并非仅仅是仁的道德气息,而是指出此气就是天地阳春之气。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也并非只是纯粹从气观仁,也同时从理观仁,故说了“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后,即说“其理便是天地生物之心”。浑然温和之气之中有理,此理即天地生物之心。人的存在本来是理气合一、浑然流行的,而现实的人必须自觉地在自己身上体现这种浑然流行,培养此种德性。如果在自家身上能体现这种仁的意思,使这个意思遍润己身,这个意思便能无间隔地流行于人己人物之间。如叶贺孙和赵致道所言,温和之气可以见仁,而温和之气的流行(流注)自然有节文(礼),自然得宜(义),自然明辨(智)。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如知福州是这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不是两人也。故明道谓:‘义礼智,皆仁也。若见得此理,则圣人言仁处,或就人上说,或就事上说,皆是这一个道理。’正叔云:‘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气象。《论语》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门人必尝理会得此一个道理。今但问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随其人而告之。……南升。(疑与上条同闻。)[32]
照这里所说,天地生发之理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就天地之生气来看,元亨利贞是气,是可见的;更容易看的是四季,春夏秋冬便是气的流行。在这里,四季的四个阶段的更换不是最重要的,四季中贯通的生育之气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气便是仁。这里所说的“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显然是指人的身心而言:朱子认为,这种人在私欲尽去后达到的温和之气,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气,这是以人合天的状态。这些都体现了朱子以温和之气为仁的思想。
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仁义礼智四德不仅仅是性理,在不同的讨论中,四德也具有其他的意义,如与存于中不同的心德说,如意思说所表达的道德信息说,如宇宙论意义的生气流行说,等。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就人心性命而言,仁既是性,也是心。虽然仁的这几层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互相否定的,而是可以共存的。
总之,上述仁论与四德论的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朱子的这些思想,使我们得以了解朱子不仅发挥继承了伊川的理学思想,也与明道的仁学思想有其内在的联系。对朱子仁学的思想,以往整体研究不够,需要更深入地分疏和诠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一是理学,一是仁学。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是我们以往关注的主体;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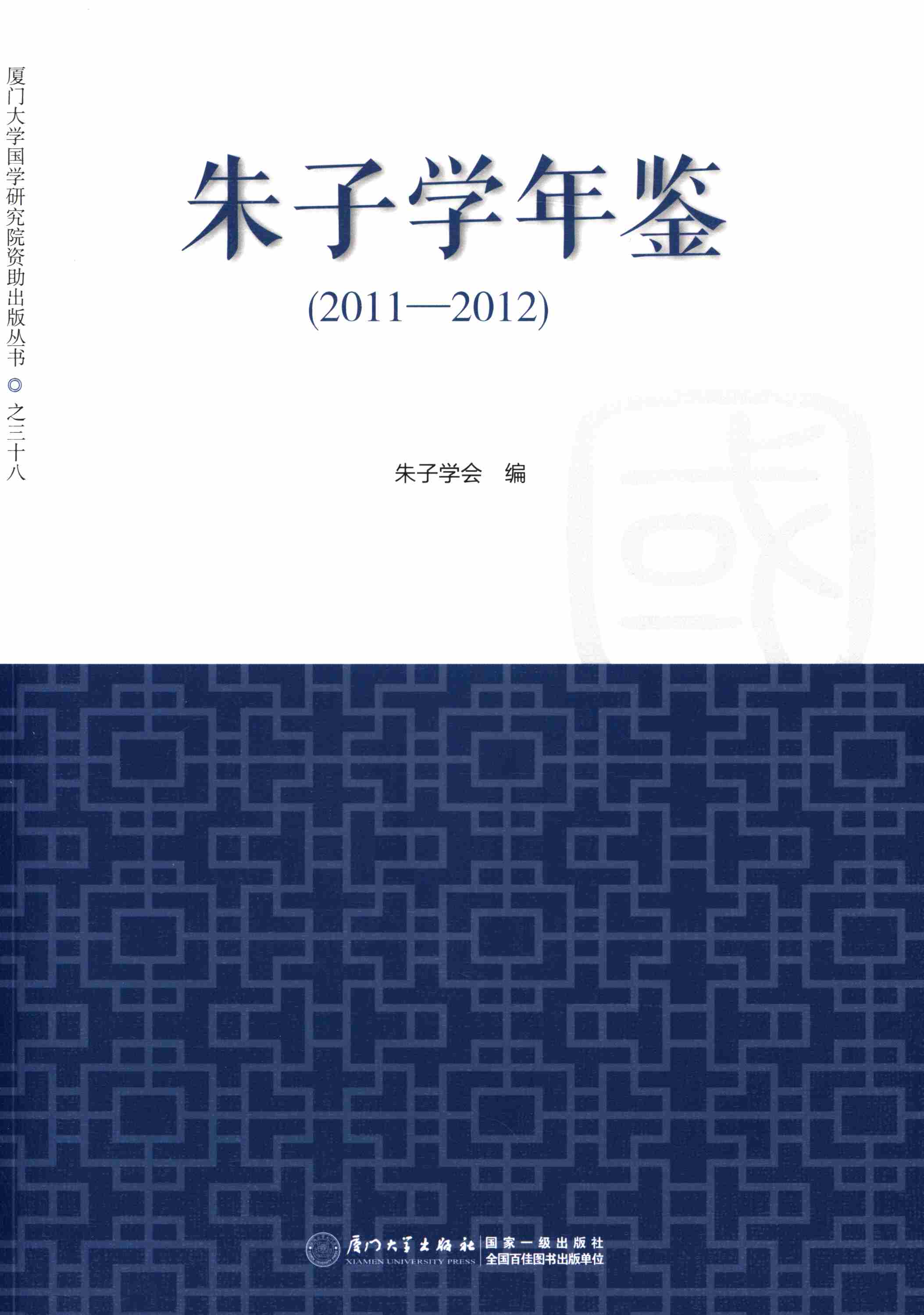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2011-2012年朱子学年鉴。内容包括本刊特稿2篇、朱子学研究新视野7篇、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6篇、朱子学研究新著38篇、朱子学书评3篇、朱子学研究优秀硕博士论文82篇、朱子学研究论文荟萃54篇、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4篇、朱子学国内外学术动态6篇、朱子学研究机构介绍3篇、朱子学研究学者介绍13篇、2011-2012年朱子学新书索引、2011-2012年朱子学论文索引556篇等。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来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