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浦安迪认为西方神话和中国神话分属不同的叙事原型,“中西神话的重要分水岭在于希腊神话可归入‘叙述性’的原型,而中国神话则属于‘非叙述性’的原型。”前者以时间性为架构的原则,后者以空间化为经营的中心,因此中国叙事缺乏细节描述,没有完整连贯的结构,注重关系和状态的描写,注重宇宙顺序和方位的安排,注重礼节的叙述等。
肖小穗(2013)发现,对浦安迪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只有林沙欧、杨矗、程金城(2009)等少数学者。但他们大多认同浦安迪的中西二分法,仅质疑他的解释,如林沙欧(2010)同意中国神话“空间化”的说法;只是认为“空间化就是中国神话元初的结构形态,并非如浦安迪所说的那样,是在中国神话发展过程中被空间化处理的结果”;杨矗(2008)从“大文化叙事”的角度进入,说明中国叙事的特点是“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六合思维指主体运思的范围,“它是上下四方(六合)立体化的,而不是线性的、片段的和平面的”,而天地境界指“本文最后或最高的‘世界图景’”。从论述中看出杨矗仍然认为中国叙事与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只是“浦安迪把缘由归结为‘先秦根深蒂固的重礼文化原型’,这观点就缺乏整体和深刻”。
在美国汉学界的一些零星讨论中,有著名学者夏志清引用《红楼梦》和其他中国小说中的例子说明中国叙事并非真如浦安迪所说关注空间多于关注时间,但说到神话时,夏志清还是觉得浦安迪的二分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同意浦安迪所说,早期中国的神话实质上是一幅静态的图景,原因是它没有提供有趣和详尽的‘行动’细节。”与夏志清不同的是,学者王瑾没有去质疑浦安迪的文本解读,她更在乎中西二分法的理论局限性。在她看来浦安迪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将所有的文学样本还原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将文学简化为某种美学的冲动”“将丰富多彩的人类戏剧代入一个非人的结构”“声称已经掌握了中国经典小说的美学原理而牺牲了文本的独特个性”。
肖小穗指出王瑾的批评缺乏文本分析的有力支持,她真正关心的不是时/空、动/静等二元模式的正当性,而是机械和不加分析地应用这些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肖小穗(2013)在其研究中透过《易经》的角度重新检视浦安迪的观点,并认为浦安迪不自觉地表现出他的“西方偏见”。主要理由为“非叙事性”的结论对中国不公平。因“注重空间”的结论背后有一系列基本假设不利于公平和适当地认识中国叙事的特点。浦安迪的论述给人一种印象:中国神话从叙事的角度看是不成熟的、不系统的和缺乏理论指导的,其“空间取向”反映了这些缺陷。他认为《易经》作为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源头,且《易经》非常讲究时间的方位布局,甚至可以说是叙述时间变化规律的艺术。中国人不是只重空间,希腊人也不是只重时间,如果说两个文化的叙事模式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重要原因是它们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手法是不同的。
上述观点在朱熹的时间观中也得到验证。在宋明理学那里“理”最主要的两个意义就是指事物的规律和道德的原则。所谓“理气关系”并不是一个本体论的生成问题,一定意义上来说乃是一个“时间”问题(郭文、李凯,2015)。这里的“时间”概念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线性的“时间”概念,而是朱熹理学的“时间”概念。由于“理”或“天理”具有先在性与永恒性,因此“理”相对于“气”是在先的,“气”是后位性的。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而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
“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己也。”这句话中所谓“道体”,若依朱熹“理”本体言之,完全可以做“天理”“理”来理解。如此一来,对于“天运而不已,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之“气”之循环往复之流行,在“天理”“道体”的照察下,此流行、生发之“气”的“时间性”就不仅具有非线性的、超时间性,也具有可溯性、可逆性的特征。
再者,浦安迪在其著作中引述诸多例子说明中国人叙事原型是非叙事性的。例如《史记》中所载“黄帝战蚩尤”:“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浦安迪认为这一记载“缺乏细节性的描绘”(1996:41),因而是缺乏叙事性的具体表现。不过肖小穗(2013)认为,此记载跳过了本来精彩的战争细节描写,但没有细节并不等于就没有叙事性。这段记载尽管简单,却已经包含了足以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故事骨架的关键字,包括“作乱”“抗命”“征师”“会战”“禽杀”,其中每一个关键字都表达了故事发展的一个个重要阶段。
研究者认为浦安迪的观点可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完全掌握中国古文叙事的言简意赅的简练特性,中国文字写景描物,时间就在其中。纵使司马迁没有交代这些细节,并不表示时间不存在,遑论浦安迪的思维缺乏中华文化的时空脉络作为参照点。
以人物为主轴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为例。《史记·夏书》:“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浦安迪认为大禹治水故事“仍然以静态的空间关系为重点”且缺乏细节(1996:45),对此研究者认为问题在于浦安迪忽视“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中的动态特性,选择性地理解本段文字。
前述两个故事被浦安迪视为非叙事性明证,可知有其偏颇之处。由此我们反而发现三个中国叙事学的基本趋向,即:1.注重关系的建构而不是个人的力量;2.注重天道而不是个人行动;3.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情感的力量。(肖小穗,2013)这三个趋向有一定的普遍性,可用于分析许多中国神话故事。分说如下:
首先是重关系、不重个体的趋向。中国叙事者注重关系的建构,不过这种关系既不纯属空间也非静态。中国人认为事件的发展取决于事件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确立因此成了叙事的关键,关系一旦确定,事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期的。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战胜蚩尤不是因为黄帝这个人了得,而是因为他在此事件中代表着正统权力和合法统治的一方,当然还因为他得到了诸侯的帮助。叙事者在故事开始时就用“乱”和“命”二字建构起蚩尤、黄帝和诸侯三者的关系。古人说的“命”还带有“天命”的含义,由此说来黄帝的权力不只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这种关系解释了黄帝为什么可以号令诸侯、擒杀蚩尤。黄帝的个人因素,譬如他的性格特征或许会影响到他出征和擒杀的方式,但却不会改变蚩尤落败被杀的命运。一般而言,关系决定了大的发展格局,与关系相比,具体的发展细节反成了“小节”,在叙事上变得不太紧要了。
其次,重天道不重个人行动,是上述两故事另一明显特点。肖小穗认为叙事必然涉及叙什么样的事——有关个人之事还是天道之事;是记录个别事实,还是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描述普遍性的事件”。中国人通常选择后者。所以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黄帝还是大禹,都有名无“实”,意思是他们只是作为某个秩序或意念的化身出现在故事之中。事件按照它应有的方式发展,如果说一开始的“作乱”有点意料之外的话,那么后续的发展便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故事中,大禹在此也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换言之关键的还不是大禹是否代表王命,而是他那套治理方法是否顺应天道。《史记·夏书》提到治水的地方有“随山浚川”“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等,这些可看作是道德正确的叙述,因为其表达了因势利导和顺天而治的理念。既然是顺天而治,读者自然相信大禹的成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最后,在这样忽略个人的大趋向下,着重道德、不着重个人情感的倾向自然浮现。上述两个故事均没有情感方面的描写,黄帝、大禹等人的个人情感在哪里?肖小穗认为中国叙事者有强大的道德倾向。因此大禹治水故事特别强调“13年”的细节。
肖小穗总结浦安迪的中西二分法偏颇并以“注重关系的建构而不是个人的力量”“注重天道而不是个人行动”“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情感的力量”三个论点来强调早期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色,进而为浦安迪对中国神话的论述诸如叙事缺乏行动细节的描述、不交代情节发展的过程、注重空间的布局等等观点提出合理的解释与反驳。
肖小穗(2013)发现,对浦安迪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只有林沙欧、杨矗、程金城(2009)等少数学者。但他们大多认同浦安迪的中西二分法,仅质疑他的解释,如林沙欧(2010)同意中国神话“空间化”的说法;只是认为“空间化就是中国神话元初的结构形态,并非如浦安迪所说的那样,是在中国神话发展过程中被空间化处理的结果”;杨矗(2008)从“大文化叙事”的角度进入,说明中国叙事的特点是“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六合思维指主体运思的范围,“它是上下四方(六合)立体化的,而不是线性的、片段的和平面的”,而天地境界指“本文最后或最高的‘世界图景’”。从论述中看出杨矗仍然认为中国叙事与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只是“浦安迪把缘由归结为‘先秦根深蒂固的重礼文化原型’,这观点就缺乏整体和深刻”。
在美国汉学界的一些零星讨论中,有著名学者夏志清引用《红楼梦》和其他中国小说中的例子说明中国叙事并非真如浦安迪所说关注空间多于关注时间,但说到神话时,夏志清还是觉得浦安迪的二分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同意浦安迪所说,早期中国的神话实质上是一幅静态的图景,原因是它没有提供有趣和详尽的‘行动’细节。”与夏志清不同的是,学者王瑾没有去质疑浦安迪的文本解读,她更在乎中西二分法的理论局限性。在她看来浦安迪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将所有的文学样本还原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将文学简化为某种美学的冲动”“将丰富多彩的人类戏剧代入一个非人的结构”“声称已经掌握了中国经典小说的美学原理而牺牲了文本的独特个性”。
肖小穗指出王瑾的批评缺乏文本分析的有力支持,她真正关心的不是时/空、动/静等二元模式的正当性,而是机械和不加分析地应用这些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肖小穗(2013)在其研究中透过《易经》的角度重新检视浦安迪的观点,并认为浦安迪不自觉地表现出他的“西方偏见”。主要理由为“非叙事性”的结论对中国不公平。因“注重空间”的结论背后有一系列基本假设不利于公平和适当地认识中国叙事的特点。浦安迪的论述给人一种印象:中国神话从叙事的角度看是不成熟的、不系统的和缺乏理论指导的,其“空间取向”反映了这些缺陷。他认为《易经》作为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源头,且《易经》非常讲究时间的方位布局,甚至可以说是叙述时间变化规律的艺术。中国人不是只重空间,希腊人也不是只重时间,如果说两个文化的叙事模式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重要原因是它们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手法是不同的。
上述观点在朱熹的时间观中也得到验证。在宋明理学那里“理”最主要的两个意义就是指事物的规律和道德的原则。所谓“理气关系”并不是一个本体论的生成问题,一定意义上来说乃是一个“时间”问题(郭文、李凯,2015)。这里的“时间”概念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线性的“时间”概念,而是朱熹理学的“时间”概念。由于“理”或“天理”具有先在性与永恒性,因此“理”相对于“气”是在先的,“气”是后位性的。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而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
“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己也。”这句话中所谓“道体”,若依朱熹“理”本体言之,完全可以做“天理”“理”来理解。如此一来,对于“天运而不已,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之“气”之循环往复之流行,在“天理”“道体”的照察下,此流行、生发之“气”的“时间性”就不仅具有非线性的、超时间性,也具有可溯性、可逆性的特征。
再者,浦安迪在其著作中引述诸多例子说明中国人叙事原型是非叙事性的。例如《史记》中所载“黄帝战蚩尤”:“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浦安迪认为这一记载“缺乏细节性的描绘”(1996:41),因而是缺乏叙事性的具体表现。不过肖小穗(2013)认为,此记载跳过了本来精彩的战争细节描写,但没有细节并不等于就没有叙事性。这段记载尽管简单,却已经包含了足以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故事骨架的关键字,包括“作乱”“抗命”“征师”“会战”“禽杀”,其中每一个关键字都表达了故事发展的一个个重要阶段。
研究者认为浦安迪的观点可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完全掌握中国古文叙事的言简意赅的简练特性,中国文字写景描物,时间就在其中。纵使司马迁没有交代这些细节,并不表示时间不存在,遑论浦安迪的思维缺乏中华文化的时空脉络作为参照点。
以人物为主轴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为例。《史记·夏书》:“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浦安迪认为大禹治水故事“仍然以静态的空间关系为重点”且缺乏细节(1996:45),对此研究者认为问题在于浦安迪忽视“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中的动态特性,选择性地理解本段文字。
前述两个故事被浦安迪视为非叙事性明证,可知有其偏颇之处。由此我们反而发现三个中国叙事学的基本趋向,即:1.注重关系的建构而不是个人的力量;2.注重天道而不是个人行动;3.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情感的力量。(肖小穗,2013)这三个趋向有一定的普遍性,可用于分析许多中国神话故事。分说如下:
首先是重关系、不重个体的趋向。中国叙事者注重关系的建构,不过这种关系既不纯属空间也非静态。中国人认为事件的发展取决于事件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确立因此成了叙事的关键,关系一旦确定,事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期的。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战胜蚩尤不是因为黄帝这个人了得,而是因为他在此事件中代表着正统权力和合法统治的一方,当然还因为他得到了诸侯的帮助。叙事者在故事开始时就用“乱”和“命”二字建构起蚩尤、黄帝和诸侯三者的关系。古人说的“命”还带有“天命”的含义,由此说来黄帝的权力不只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这种关系解释了黄帝为什么可以号令诸侯、擒杀蚩尤。黄帝的个人因素,譬如他的性格特征或许会影响到他出征和擒杀的方式,但却不会改变蚩尤落败被杀的命运。一般而言,关系决定了大的发展格局,与关系相比,具体的发展细节反成了“小节”,在叙事上变得不太紧要了。
其次,重天道不重个人行动,是上述两故事另一明显特点。肖小穗认为叙事必然涉及叙什么样的事——有关个人之事还是天道之事;是记录个别事实,还是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描述普遍性的事件”。中国人通常选择后者。所以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黄帝还是大禹,都有名无“实”,意思是他们只是作为某个秩序或意念的化身出现在故事之中。事件按照它应有的方式发展,如果说一开始的“作乱”有点意料之外的话,那么后续的发展便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故事中,大禹在此也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换言之关键的还不是大禹是否代表王命,而是他那套治理方法是否顺应天道。《史记·夏书》提到治水的地方有“随山浚川”“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等,这些可看作是道德正确的叙述,因为其表达了因势利导和顺天而治的理念。既然是顺天而治,读者自然相信大禹的成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最后,在这样忽略个人的大趋向下,着重道德、不着重个人情感的倾向自然浮现。上述两个故事均没有情感方面的描写,黄帝、大禹等人的个人情感在哪里?肖小穗认为中国叙事者有强大的道德倾向。因此大禹治水故事特别强调“13年”的细节。
肖小穗总结浦安迪的中西二分法偏颇并以“注重关系的建构而不是个人的力量”“注重天道而不是个人行动”“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情感的力量”三个论点来强调早期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色,进而为浦安迪对中国神话的论述诸如叙事缺乏行动细节的描述、不交代情节发展的过程、注重空间的布局等等观点提出合理的解释与反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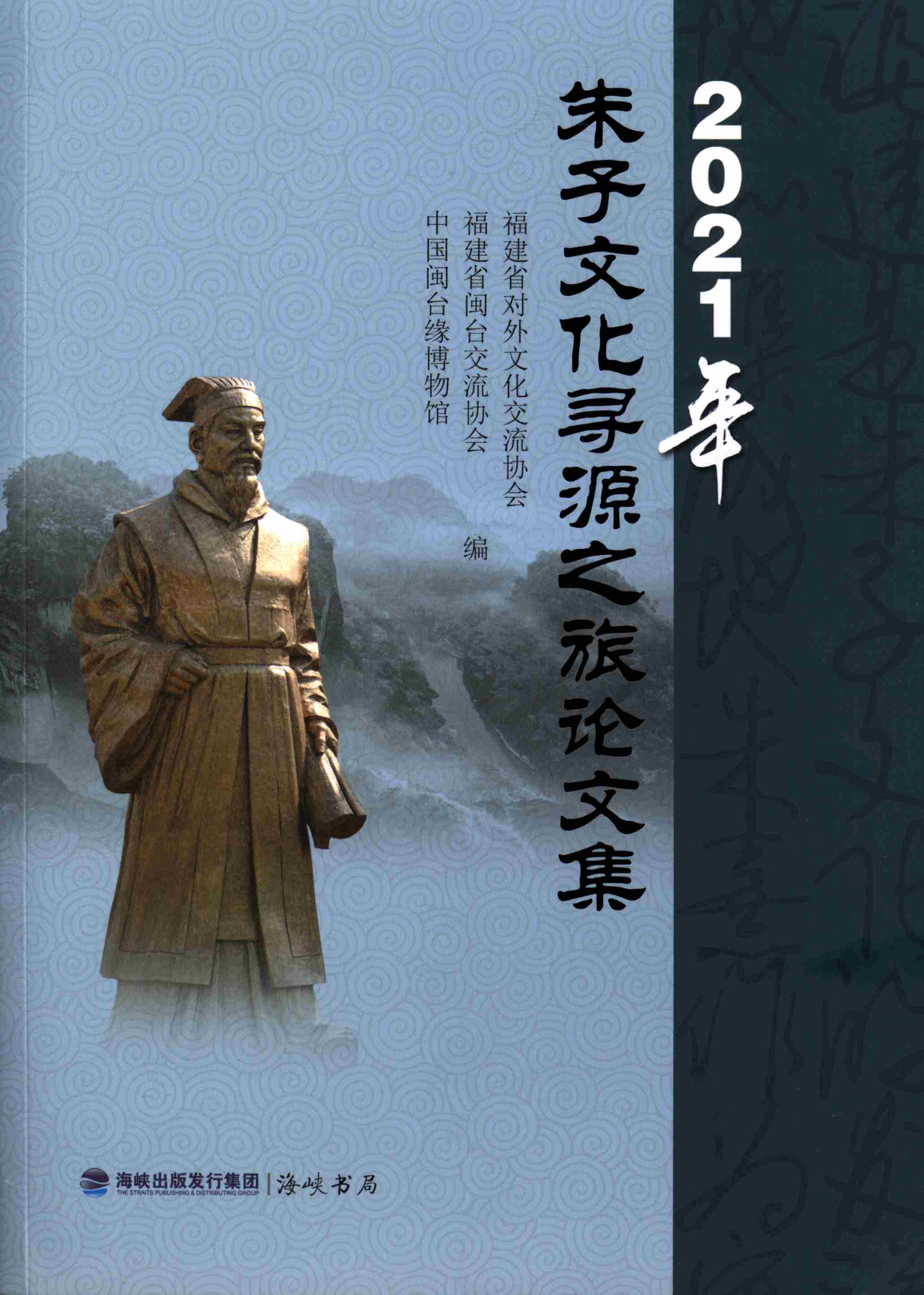
《2021年朱子文化寻源之旅论文集》
出版者:海峡书局
本书收录了《展现福建传承弘扬朱子文化新气象》《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朱熹的民本思想》《武夷山朱子文化旅游价值与建设路径》《民本视域下的朱子慈善思想及其实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浦安迪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