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对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2021年朱子文化寻源之旅论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158 |
| 颗粒名称: | 朱熹理学对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5 |
| 页码: | 093-107 |
| 摘要: | 本文记述阳明心学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亦呈现出明显的进路阶段性。若以“龙场悟道”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可以说,从王阳明前期探究朱熹理学思想到“龙场悟道”的思想转折、创立心学,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探究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历程是无法也不可能绕开朱熹理学思想的。正因为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有20余年的潜心研习、洞察精微,才有可能创立良知心学的为学进路。朱熹理学成为阳明心学在学理上标新立异的逻辑前提及切入点。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前,其深受朱熹理学环境的影响和浸润:一是明代“是朱非陆”学风的影响,二是余姚地域文化崇朱学传统的影响,三是姚江秘图山王氏家学传统的浸润等。就阳明本身的为学进程而言,主要是受朱熹的“天理”观、“修身”观的影响,这可从王阳明所撰的《山东乡试录》程式文中得到明证。阳明心学的创立并非以朱熹理学为对立面而存在,更不是对朱熹理学的反动,纵观朱王学说体系,前后之间在学理上仍有诸多同质性的联系。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学术思想认识路径上的分歧,而非道德伦理目的追求上的分野,这也成为“朱王会通”在学理上的逻辑基础与学术研究深化的前提。 |
| 关键词: | 朱熹 王阳明 思想进路 影响 |
内容
任何思想学说的形成均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有它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及转折点,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也不例外,有一个很长的孕育、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就其阶段性而言,若以“龙场悟道”作为其思想发展的转折期,则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内又可分为若干个发展的小阶段。王阳明前期的思想探索离不开与朱熹理学(或称之为“道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外部环境说,自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传统等有关;从其学理的进路说,主要应在“天道观”和“修身观”等几个方面。深入研究王阳明前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正确诠释朱学、阳明学之间的内在理路,全面、完整、正确地解读阳明心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朱熹理学对余姚地域文化的影响
王阳明所生活的明代中期,朱熹理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极大多数官员、学子认可的思想观念。当时学界的现状,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言:“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1]文中所说的“先儒之成说”显然是指“程朱理学”,主要表现即为弥漫于学界、官场的“述朱”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思想主控意识形态的状况。在王阳明的故乡——浙东余姚,同样是朱学传播与浸润的重镇。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童年时代,十岁时离开故乡赴京求学,[2]此后,数度返归故里。余姚作为其生命的根系所在,是其精神栖居的家园,亦是其接受朱学最初的土壤。
首先,姚地因读书风气之盛而称誉绍郡八邑,诸多学子读书以参加科举、出仕为荣,读书、举业几乎成为大多数学子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社会中,科考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考生的必读书,又是考官判卷取士的主要依据。因此,余姚士子的工夫大多下在攻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整个社会亦沾被朱学风气。明末文学家绍兴山阴人张岱在《夜航船·序》中特别点到余姚学子的读书风气:“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3]张岱的上述说法,虽存在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姚籍士子以参加科举为取向的读书状况。正因为这种浓郁的读书之风,其效果必然在学子获取功名的数据上反映出来。据清光绪《余姚县志》等史料统计:有明一代,姚籍士子考中进士者多达389人,[4]这些中试者均为深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学子,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余姚一地受朱学濡化的程度之深,难怪大学者梁启超赞评:“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5]梁启超的这一评语中自然包括了像王阳明等众多的科举人物,这也说明科举人物并不一定个个都是思想僵化、毫无建树、只会死读书的“两脚书厨”。王阳明在理学风气浓郁的余姚地域环境中接受启蒙教育,耳濡目染,说法,阳明赴京师在成化十八年,时年十一岁。然而,据阳明本人所撰《送绍兴佟太守序》一文中载:“成化辛丑(1481),予来京师,居长安西街。”(参见《王文成公全书·续编四》卷二十九)“成化辛丑”,即成化十七年(1481)。时年,王阳明才十岁,比钱说早一年。本文中关于此时间的确定,从王阳明本人所言。这对其“学成圣贤”志向的确立不无关系,余姚亦是其思想探索的起点。
其次,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的家学传承以儒学为主、这自然也包含朱子学的滋养。王阳明祖上奉行儒家处世为人的基本伦理准则,恪守“忠、孝、悌、忍、信”之伦理纲要,讲究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阳明之父王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科业有成,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以布衣魁天下”,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恪守儒教传统,忠孝两全,堪称楷模。王华处世为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尤其是他的慈孝精神,对其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华对家族成员的教育重在理学思想的传承,并内化为家族的礼仪门风。阳明自幼受祖父王伦的庭训,十岁时赴京求学,又在父亲身边侍学,研习朱熹理学,这对王阳明一生的道德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的青少年时代深受朱学思想的濡化。
另据清光绪《余姚县志》记载:阳明之父王华与同邑状元谢迁、榜眼黄珣、名儒陆恒等人交往甚密,这些人入仕前均为攻读朱学的士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少年王阳明的为学之路。
再次,朱熹的足迹曾到过余姚,余姚亦是朱学的流播之地。南宋淳熙八年(1181)七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江西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据《余姚四明黄氏宗谱》记载:朱熹在浙东路任职期间,曾应余姚梁弄乡贤黄道贲邀请到九姥山道院讲学,宗谱中记载了这件事,[6]这说明朱熹对余姚是有直接影响的。就王阳明而言,其晚年在家乡传道受到朱学势力的阻力,这可从相关史料中得到证实。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归余姚故里省祖茔,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姚籍学子钱德洪久仰阳明先生的道德文章、事功盖世,久思及门;但乡中那些执着于朱学的耆老对阳明心学颇为疑心,然钱德洪经过暗中观察后,对王阳明良知学说深信不疑,乃力排众议,还带领侄子及74个姚籍弟子拜王阳明为师。在拜王阳明为师的这些学子中很多均有朱学的背景。由此可知,即便到了阳明心学已风靡大江南北之时,在阳明故里朱学阵营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明末清初,大学者姚人黄宗羲以传承阳明心学为己任,而另一大学者姚人朱舜水则以朱学为圭臬,传道东瀛。这说明明中期以降,朱、王两大思想阵营在余姚的并峙与流播。
总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及家学等多因素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朱学在姚地的流播是考察王阳明求道进路的重要前提,否则,就难以真正解读阳明心学创立的时代、地域和学术背景。
二、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自觉探求
王阳明自启蒙始就接受程朱理学的熏陶,直至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悟道”前,其思想进路轨迹是以朱熹理学为主导的,主要考察点为:
一是其少年时就立下“学成圣贤”之志,这成为其内生性的求道动因和人生价值目标追求。二是十七岁时[7],迎新婚妻子诸氏自南昌返姚经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大儒娄谅,得到娄谅指点,深契“圣人必可学而至”,按娄谅的教诲前行不疑。明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阳明中浙江乡试后,专攻朱熹“格物之学”。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待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众’。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8]从“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语可知,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研究是下了苦工的,但终因其对朱熹“格物”之论的内涵产生误解,“格竹”求道导致失败,王阳明一时陷入了思想困顿,便假托“圣贤有分”而“随世就辞章之学”,这应是王阳明为学路上的一次思想探求的挫折。尽管年轻的王阳明在“学成圣贤”的思想探索道路上对朱熹“格物之学”难以参透、产生怀疑之念;但总体上还是在朱熹理学的进路上前行。直至王阳明二十七岁,即中进士的前一年,他仍在啃读朱熹的著述,且对自己“为学成圣贤”之进路有所反思。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9]由于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体用工夫之说尚未悟透,怀疑朱熹的思想支离了“物理”“学理”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又概叹“圣贤有分”“遂有遗世入山之意”。王阳明在“为学成圣”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应该说是对朱熹“格物说”不能参透的内心烦恼。王阳明入仕后,仍然是沿着宋儒的理路前行。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奉命在江北录囚后,专门上九华山访道。在地藏洞遇异人问道,经异人开示:“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事后,王阳明再次问道未果,于是发“会心人远”之叹。可见,王阳明亦把周、程作为所崇尚的先儒,仍执著于理学。
王阳明对宋儒之学的研修功力之深不仅反映在学问的长进上,而且更体现在对宋儒“天理”观的践行上,有两件事可证。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时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因病告假归越,在宛委山阳明洞天修炼导引术,因静坐之法而起离世之念;但终因孝亲之念未断而毅然舍弃出世之念,这是王阳明用“天理”战胜“出世”之念的自身救赎,也可以说是对朱熹“天理”观的一次精神回归。王阳明在阳明洞天修炼的思想升华,显示其在思想探索上从向先儒所撰的经典中求道转向从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上求道,而这一转变往往被当代的论者所忽视。另一件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六年,王阳明从绍兴城南宛委山移疾杭州西湖,养病净寺、虎跑寺之间,用“爱亲本性”之论开示坐关僧人还家孝亲,由此实现了推己及人的“天理”之本性,亦成为弘治十七年应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邀主试山东乡试撰写程式文之底气。弘治十八年,王阳明依据自己对孔孟儒学及宋儒理学的把握开始授徒讲学,并结交翰林院庶吉士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共倡圣学,这标志着王阳明对孔孟儒学、象山心学与程朱理学的重新审视及梳理,为“龙场悟道”奠定了必要的学理基础,而促成阳明心学生发的外因则是正德元年(1506)发生在朝中的反阉党斗争。
通过以上对王阳明思想探索历程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自十岁立志“学成圣贤”始至正德元年反阉党斗争的失败、被贬谪贵州龙场驿这二十余年中,王阳明的思想探索始终与朱熹理学相伴随,科业、佛道、文学、兵学、书艺等均没有成为王阳明精神栖居的田园,而朱熹理学是其所寻求的主要思想资源,而这一切又成为“龙场悟道”发生的支点,也成为世人解读“阳明心学”的理论枢纽。
三、朱熹“天理”学说对王阳明“天道”观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们为建构庞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完成终极性的理论架构,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本体论、工夫论概念,并做了系统的论证。如北宋理学宗主周敦颐提出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等学说,而南宋陆九渊则提出了“心即理”学说。比较而言,南宋朱熹的“天理”观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认为:“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仁义理智是天理之件数。”[10]从中可知,朱熹的“天理”观要旨是反映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具有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指向。故不能认为朱熹对“天理”含义的诠释仅仅是指专为维护专制社会三纲五常伦理服务的。朱熹还认为天地之间存在形上之“道”和形下之“气”。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据朱熹这一解释,世界万物具有“道”与“器”的属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朱熹又认为:“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11]朱熹的这一解释,从道德判断的角度上看揭示了作为认识主体之“心”是内敛性的,“天理”是“心”之“本然”状态。道德认识与道德判断的正确与否,能充分反映出“心”体与“天理”之间的互通关系。上述三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的。
朱熹的“天理”观,从逻辑上说对王阳明的“天道”观是有重要影响的。在理论形式表现上更具现实性和导向性。所谓“天道”,可理解为宇宙运行的本然状态,或称为宇宙本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先儒们往往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天道,因此有了自己的特色。所谓“大人之道”,即指那些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天道”的把握和诠释、发挥,以及进行思想、文化呈现形式的创设,诸如“八卦图”之类。后世学者对先人所描述的“天道”观之诠释越来越精细,从而形成严密的理学体系。
王阳明因长期受朱熹“天理”观影响,对朱熹的“天理”观做了独到的发挥,并以“天道”作为论题。诸如,其在任山东乡试主考时,据《易经》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一题,在程文(主考官所拟范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天道”与“大人之道”之间的关系,并做了深刻、辩证的论述。王阳明认为:
自其先于天者言之,时之未至,而道隐于无,天未有为也,大人则先天而为之。盖必经纶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与道符;裁成以创其始,而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与天之所叙者,有吻合焉;五礼未制也,以义起之,而与天之所秩者,无差殊焉。天何尝与之违乎?以其后于天者言之,时之既至,而理显于有,天已有为也,大人则后天而奉之。盖必穷神以继其志,而理之固有者,只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当行者,钦若之而不违。如天叙有典也,立为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礼也,制为品节以齐之,五礼自我而庸矣。我何尝违于天乎?是则先天不违,大人即天也;后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与天,其可以二视之哉?[12]
王阳明所论证的“天道”是立足于“大人”的角度,是对《易经》“天道”思想的体悟与把握,突出了“大人”对于“天道”的感应性、解释性。“大人”的境界先天明觉,不仅体悟天道,而且替天道行事,即“大人”至大至圣,在于能先人而悟天道,具有把握天道之能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王阳明所论证的“天道”或谓之“天理”,其内涵是指宇宙的本然状态,属于本体的问题,即“形有不同,道则无异”。“天道”是无形的,然“大人”能发其端倪。王阳明将“天道”与“大人之道”合二为一,实际是在论说圣人对于天道的领悟及天道在万事万物中的显现。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预测未来,只要将“天道”贯穿始终,就能顺应天时地利,自强不息,而“大人”在体悟天道的同时还承担着传道弘法的重任。王阳明在程式文中将深奥的“天道”精义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达,以开示考生。王阳明借助《易经》对“天道”观的阐发,亦是对朱熹“天理”观的发挥。王阳明对“天道”观的表述是十分严谨的,以此启发考生欲达“大人”之境界,就必须深悟儒家经典与“天道”之间的内在关系,明觉“大人”在开显、表述“天道”中的主宰作用,这一思想与王阳明其后所论证的“万物一体”思想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王阳明看来,绝不能把“为学成圣”与“存天理,灭人欲”两者对立起来,甚至当作两件事加以支离。在此文末,王阳明还用反问句作结:“大人与天,其可以二视之哉?”其结论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显然,王阳明对借《易经》阐发“先天”与“后天”的认识,源于儒家的天道观念,但王阳明在程式文中大大深化了这一思想,别出心裁,发人之所未发。王阳明将“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内在关系做了综合的判断,并将这一思想引入道德世界,化奥义为简明,体现了王阳明天道思想的简切明达。王阳明的天道思想,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不同意人为地割裂“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内在联系、以及反对将“天理”绝对化。正因为世儒对各种名利、欲望的渴求,人欲泛滥,最后导致人们发现“天道”的能力被弱化,心体被遮蔽,如此就很难开显出合乎天道的道德境界。王阳明还根据《易经》,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命题,通过河图、洛书与八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万物统一的“天道”问题,揭示“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同一性,这与朱熹的“天理”观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的,其共同点是都将“天理”或称之为“道”,指向道德意义世界。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在乡试程式文中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朱熹的“天理”观,两者之间是可以贯通的。相对来说,“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在理论形式上表现更具外在性与现实性,王阳明传承了这一思想,但主要侧重点在“天道”与“大人之道”的贯通方面,而不是着眼于具体的微观层面而已。
四、朱熹“诚意”学说对王阳明“修身”观的影响
“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炼要求,也是“立志”进德的自律途径,是《大学》中所列“八条目”之一。汉唐以来的儒学主要以训释经典为治学门径,对“修身”之道的学理探究则不太重视。到了宋代,理学家们不光继承了汉儒对经典训释的传统,还特别注重对先圣经典中关于“修身”义理的诠释,并引入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身之路。
朱熹在治学与教育方法上,要求学子直接面对经典而导入生命的过程,以回应社会所关注的伦理道德秩序问题,尤其强调人伦纲常需落实在生活细节中。朱熹认为:“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13]此言,揭示了“修身”是内敛的功夫,以“正心”为导向。重点在日常人际关系中加以自律,在言行上加以审察,及时改过,而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主要功夫,以“修身”为本。就方式而言,在言谈举止上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及情感的表达,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朱熹认为:“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14]朱熹的这一修身思想与王阳明的“修身”观内涵互补,相辅相成,只不过王阳明在表述上更加缜密,发挥更具神采。
立志修身,是王阳明道德修炼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思想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进入仕途后,省察自悟,学问思辨,在修身实践上深有所得,并将这种体悟作为引领学子“修身”观的价值理想。诸如,其在任山东乡试主考时,在试题中将“修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考察考生。王阳明据《中庸》出题:“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在程文中,王阳明阐述了修身的关键在于“尽持敬之功”。指出“九经”之本在于“修身”,又将修身分为“内修”与“外修”之统一,并以“孔子告哀公之问政”一事借题发挥:
“九经”莫重于修身,修身惟在于主敬。诚使内志静专,而罔有错杂之私,中心明洁,而不以人欲自蔽,则内极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严;垂绅正笏,而俨然威仪之整肃,则外极其检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复礼,而所行皆中夫节。不但存之静也,遏人欲于方萌,而所由不睽于礼,尤必察之于动也,是则所谓尽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以修身哉?诚以不一其内,则无以制其外;不齐其外,则无以养其中,修身之道未备也。静而不存,固无以立其本;动而不察,又无以胜其私,修身之道未尽也。今焉,制其精一于内,而极其检束于外,则是内外交养,而身无不修矣。行必以礼,而不戾其所存;动必以正,所而不失其所养,则是动静不违,而身无不修矣。是则所谓端“九经”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于持敬哉?大抵“九经”之序,以身为本;而圣学之要,以敬为先,能修身以敬,则笃恭而天下平矣。[15]
上述,王阳明将“内修”定义为“主敬”,而“主敬”则是“内志静专”“中心明洁”,将“外修”与“内修”联系起来。又将“外修”定义为:“穆然容止之端严”“俨然威仪之整肃”,认为人的仪容仪表“端庄”有“克己复礼”之约束力;而“内修”则为不以人欲自蔽。内外统一,动静结合,即能存静遏欲,合乎于礼。修身之道,以身为本,以敬为先,以实现天下太平、和合社会之理想。王阳明还将修身与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较透彻的论证。考其思想源头,是对《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思想的回应,这与《大学》要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完全一致的。修身的关键在于立志,这也是王阳明人生态度和思想探索的重要方面。王阳明还在山东乡试策问中据《中庸》出:“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诸君皆志伊学颜者,请遂以二君之事质之。”在程式文中,王阳明将古代圣贤伊尹之志和颜子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阐明了人生的境界是“箪瓢之乐”:
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能穷理,故能择乎中庸,而复理以为仁;能慎独,故能克己不贰过,而至于三月不违。盖其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宽体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后能知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也,然后能知颜子之学。生亦何能与于此哉?顾其平日亦在所不敢自暴自弃,而心融神会之余,似亦微有所见。[16]
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的“慎独”。只有通过内心的修养,才能达到内圣,只有做到内圣,方能够治国安邦,达到外王的目的。因此,王阳明十分推崇孔门弟子颜回的“内圣”精神,自我主宰,独立独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同时,王阳明也十分敬仰商初大臣伊尹的才德。告诫学子,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都要以修身养德为要,内具圣道,外施王道,师范天下。王阳明将伊尹之志和颜子之学作为自身道德修炼的楷模,体现了道德观与政治观的统一,“修己”与“治国”的结合,体现了《大学》三纲领的基本要求。相对而言,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王阳明不仅推崇“箪瓢之乐”的人生境界;而且对伊尹“见细微于平常”的“修己”与“治国”相结合的“修身”进路同样赞赏,这是其“修身”思想探索的重要内容,更是其立身的准则。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在《题汤大行殿试策问下》中对“修身”思想的论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汤者数言,而终身践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数言,而终身践之。推其心也,君其志于伊、吕之事乎?夫辉荣其一时之遭际以夸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则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鉴也。昔人有恶形而恶鉴者,遇之则将掩袂却走。君将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乌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于伊、吕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17]
在上述题辞中,王阳明十分强调为官者当有“伊、吕”之志,必须做到“言行一致”“以言为鉴”,即以自己所言对照自己所行,摒弃那种口是心非,知行二分的“伪君子”行径。可见,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程式文中对“修身”的阐述,与朱熹的“修身观”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程式文中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发挥而己。在修身学说上,朱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逻辑性的哲学范畴,构建了一套严密的道德本体论、认识论和工夫论体系,代表性的学说是“格物论”,即“格物穷理”。尽管“格物论”的逻辑外延十分宏阔,但其中自然包含了儒家的修身之论。王阳明年轻时,因深受朱熹修身”诚意”观的影响,在自身道德修炼中虽有不少困惑,但总体上对朱熹的修身观是接纳、融通的。
结语
综上言之,对王阳明前期思想发展进路的考察,朱熹理学对王阳明心路历程的影响十分密切,这为其“阳明心学”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若离开这一发展阶段也无法说清楚“阳明心学”产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是前后联系的。从对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深入探究中,可以明显发现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在诸多方面是深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的,这可为深入研究阳明学提供某些方向性、前瞻性和基础性的学术视角。同时,通过探究王阳明前期的思想发展进路也可反观朱熹思想的丰富性、独特性,为世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观察点。阳明心学是在对朱学的发明、碰撞中逐步开新出来的,尤其是对朱熹“格物”学说的辩证,是阳明心学生发的一个切入点。在王阳明的那个时代,无论是信奉程朱理学还是信奉陆王心学的学人,一般来说,都具有包容的心态,亦师亦友,相互辩难,即使学术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但私谊如故。可以说,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中一直伴随着对朱熹学说的接受与质疑、批评与开新,方成其大。阳明心学的发生是因朱熹的“格物”学说而起,朱熹学说作为潜在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范式,从方方面面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两者的融通,无论对研究朱熹理学还是研究阳明心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朱熹理学对余姚地域文化的影响
王阳明所生活的明代中期,朱熹理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极大多数官员、学子认可的思想观念。当时学界的现状,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言:“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1]文中所说的“先儒之成说”显然是指“程朱理学”,主要表现即为弥漫于学界、官场的“述朱”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思想主控意识形态的状况。在王阳明的故乡——浙东余姚,同样是朱学传播与浸润的重镇。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童年时代,十岁时离开故乡赴京求学,[2]此后,数度返归故里。余姚作为其生命的根系所在,是其精神栖居的家园,亦是其接受朱学最初的土壤。
首先,姚地因读书风气之盛而称誉绍郡八邑,诸多学子读书以参加科举、出仕为荣,读书、举业几乎成为大多数学子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社会中,科考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考生的必读书,又是考官判卷取士的主要依据。因此,余姚士子的工夫大多下在攻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整个社会亦沾被朱学风气。明末文学家绍兴山阴人张岱在《夜航船·序》中特别点到余姚学子的读书风气:“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3]张岱的上述说法,虽存在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姚籍士子以参加科举为取向的读书状况。正因为这种浓郁的读书之风,其效果必然在学子获取功名的数据上反映出来。据清光绪《余姚县志》等史料统计:有明一代,姚籍士子考中进士者多达389人,[4]这些中试者均为深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学子,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余姚一地受朱学濡化的程度之深,难怪大学者梁启超赞评:“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5]梁启超的这一评语中自然包括了像王阳明等众多的科举人物,这也说明科举人物并不一定个个都是思想僵化、毫无建树、只会死读书的“两脚书厨”。王阳明在理学风气浓郁的余姚地域环境中接受启蒙教育,耳濡目染,说法,阳明赴京师在成化十八年,时年十一岁。然而,据阳明本人所撰《送绍兴佟太守序》一文中载:“成化辛丑(1481),予来京师,居长安西街。”(参见《王文成公全书·续编四》卷二十九)“成化辛丑”,即成化十七年(1481)。时年,王阳明才十岁,比钱说早一年。本文中关于此时间的确定,从王阳明本人所言。这对其“学成圣贤”志向的确立不无关系,余姚亦是其思想探索的起点。
其次,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的家学传承以儒学为主、这自然也包含朱子学的滋养。王阳明祖上奉行儒家处世为人的基本伦理准则,恪守“忠、孝、悌、忍、信”之伦理纲要,讲究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阳明之父王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科业有成,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以布衣魁天下”,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恪守儒教传统,忠孝两全,堪称楷模。王华处世为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尤其是他的慈孝精神,对其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华对家族成员的教育重在理学思想的传承,并内化为家族的礼仪门风。阳明自幼受祖父王伦的庭训,十岁时赴京求学,又在父亲身边侍学,研习朱熹理学,这对王阳明一生的道德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的青少年时代深受朱学思想的濡化。
另据清光绪《余姚县志》记载:阳明之父王华与同邑状元谢迁、榜眼黄珣、名儒陆恒等人交往甚密,这些人入仕前均为攻读朱学的士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少年王阳明的为学之路。
再次,朱熹的足迹曾到过余姚,余姚亦是朱学的流播之地。南宋淳熙八年(1181)七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江西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据《余姚四明黄氏宗谱》记载:朱熹在浙东路任职期间,曾应余姚梁弄乡贤黄道贲邀请到九姥山道院讲学,宗谱中记载了这件事,[6]这说明朱熹对余姚是有直接影响的。就王阳明而言,其晚年在家乡传道受到朱学势力的阻力,这可从相关史料中得到证实。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归余姚故里省祖茔,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姚籍学子钱德洪久仰阳明先生的道德文章、事功盖世,久思及门;但乡中那些执着于朱学的耆老对阳明心学颇为疑心,然钱德洪经过暗中观察后,对王阳明良知学说深信不疑,乃力排众议,还带领侄子及74个姚籍弟子拜王阳明为师。在拜王阳明为师的这些学子中很多均有朱学的背景。由此可知,即便到了阳明心学已风靡大江南北之时,在阳明故里朱学阵营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明末清初,大学者姚人黄宗羲以传承阳明心学为己任,而另一大学者姚人朱舜水则以朱学为圭臬,传道东瀛。这说明明中期以降,朱、王两大思想阵营在余姚的并峙与流播。
总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及家学等多因素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朱学在姚地的流播是考察王阳明求道进路的重要前提,否则,就难以真正解读阳明心学创立的时代、地域和学术背景。
二、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自觉探求
王阳明自启蒙始就接受程朱理学的熏陶,直至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悟道”前,其思想进路轨迹是以朱熹理学为主导的,主要考察点为:
一是其少年时就立下“学成圣贤”之志,这成为其内生性的求道动因和人生价值目标追求。二是十七岁时[7],迎新婚妻子诸氏自南昌返姚经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大儒娄谅,得到娄谅指点,深契“圣人必可学而至”,按娄谅的教诲前行不疑。明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阳明中浙江乡试后,专攻朱熹“格物之学”。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待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众’。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8]从“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语可知,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研究是下了苦工的,但终因其对朱熹“格物”之论的内涵产生误解,“格竹”求道导致失败,王阳明一时陷入了思想困顿,便假托“圣贤有分”而“随世就辞章之学”,这应是王阳明为学路上的一次思想探求的挫折。尽管年轻的王阳明在“学成圣贤”的思想探索道路上对朱熹“格物之学”难以参透、产生怀疑之念;但总体上还是在朱熹理学的进路上前行。直至王阳明二十七岁,即中进士的前一年,他仍在啃读朱熹的著述,且对自己“为学成圣贤”之进路有所反思。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9]由于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体用工夫之说尚未悟透,怀疑朱熹的思想支离了“物理”“学理”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又概叹“圣贤有分”“遂有遗世入山之意”。王阳明在“为学成圣”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应该说是对朱熹“格物说”不能参透的内心烦恼。王阳明入仕后,仍然是沿着宋儒的理路前行。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奉命在江北录囚后,专门上九华山访道。在地藏洞遇异人问道,经异人开示:“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事后,王阳明再次问道未果,于是发“会心人远”之叹。可见,王阳明亦把周、程作为所崇尚的先儒,仍执著于理学。
王阳明对宋儒之学的研修功力之深不仅反映在学问的长进上,而且更体现在对宋儒“天理”观的践行上,有两件事可证。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时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因病告假归越,在宛委山阳明洞天修炼导引术,因静坐之法而起离世之念;但终因孝亲之念未断而毅然舍弃出世之念,这是王阳明用“天理”战胜“出世”之念的自身救赎,也可以说是对朱熹“天理”观的一次精神回归。王阳明在阳明洞天修炼的思想升华,显示其在思想探索上从向先儒所撰的经典中求道转向从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上求道,而这一转变往往被当代的论者所忽视。另一件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六年,王阳明从绍兴城南宛委山移疾杭州西湖,养病净寺、虎跑寺之间,用“爱亲本性”之论开示坐关僧人还家孝亲,由此实现了推己及人的“天理”之本性,亦成为弘治十七年应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邀主试山东乡试撰写程式文之底气。弘治十八年,王阳明依据自己对孔孟儒学及宋儒理学的把握开始授徒讲学,并结交翰林院庶吉士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共倡圣学,这标志着王阳明对孔孟儒学、象山心学与程朱理学的重新审视及梳理,为“龙场悟道”奠定了必要的学理基础,而促成阳明心学生发的外因则是正德元年(1506)发生在朝中的反阉党斗争。
通过以上对王阳明思想探索历程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自十岁立志“学成圣贤”始至正德元年反阉党斗争的失败、被贬谪贵州龙场驿这二十余年中,王阳明的思想探索始终与朱熹理学相伴随,科业、佛道、文学、兵学、书艺等均没有成为王阳明精神栖居的田园,而朱熹理学是其所寻求的主要思想资源,而这一切又成为“龙场悟道”发生的支点,也成为世人解读“阳明心学”的理论枢纽。
三、朱熹“天理”学说对王阳明“天道”观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们为建构庞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完成终极性的理论架构,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本体论、工夫论概念,并做了系统的论证。如北宋理学宗主周敦颐提出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等学说,而南宋陆九渊则提出了“心即理”学说。比较而言,南宋朱熹的“天理”观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认为:“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仁义理智是天理之件数。”[10]从中可知,朱熹的“天理”观要旨是反映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具有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指向。故不能认为朱熹对“天理”含义的诠释仅仅是指专为维护专制社会三纲五常伦理服务的。朱熹还认为天地之间存在形上之“道”和形下之“气”。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据朱熹这一解释,世界万物具有“道”与“器”的属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朱熹又认为:“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11]朱熹的这一解释,从道德判断的角度上看揭示了作为认识主体之“心”是内敛性的,“天理”是“心”之“本然”状态。道德认识与道德判断的正确与否,能充分反映出“心”体与“天理”之间的互通关系。上述三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的。
朱熹的“天理”观,从逻辑上说对王阳明的“天道”观是有重要影响的。在理论形式表现上更具现实性和导向性。所谓“天道”,可理解为宇宙运行的本然状态,或称为宇宙本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先儒们往往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天道,因此有了自己的特色。所谓“大人之道”,即指那些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天道”的把握和诠释、发挥,以及进行思想、文化呈现形式的创设,诸如“八卦图”之类。后世学者对先人所描述的“天道”观之诠释越来越精细,从而形成严密的理学体系。
王阳明因长期受朱熹“天理”观影响,对朱熹的“天理”观做了独到的发挥,并以“天道”作为论题。诸如,其在任山东乡试主考时,据《易经》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一题,在程文(主考官所拟范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天道”与“大人之道”之间的关系,并做了深刻、辩证的论述。王阳明认为:
自其先于天者言之,时之未至,而道隐于无,天未有为也,大人则先天而为之。盖必经纶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与道符;裁成以创其始,而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与天之所叙者,有吻合焉;五礼未制也,以义起之,而与天之所秩者,无差殊焉。天何尝与之违乎?以其后于天者言之,时之既至,而理显于有,天已有为也,大人则后天而奉之。盖必穷神以继其志,而理之固有者,只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当行者,钦若之而不违。如天叙有典也,立为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礼也,制为品节以齐之,五礼自我而庸矣。我何尝违于天乎?是则先天不违,大人即天也;后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与天,其可以二视之哉?[12]
王阳明所论证的“天道”是立足于“大人”的角度,是对《易经》“天道”思想的体悟与把握,突出了“大人”对于“天道”的感应性、解释性。“大人”的境界先天明觉,不仅体悟天道,而且替天道行事,即“大人”至大至圣,在于能先人而悟天道,具有把握天道之能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王阳明所论证的“天道”或谓之“天理”,其内涵是指宇宙的本然状态,属于本体的问题,即“形有不同,道则无异”。“天道”是无形的,然“大人”能发其端倪。王阳明将“天道”与“大人之道”合二为一,实际是在论说圣人对于天道的领悟及天道在万事万物中的显现。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预测未来,只要将“天道”贯穿始终,就能顺应天时地利,自强不息,而“大人”在体悟天道的同时还承担着传道弘法的重任。王阳明在程式文中将深奥的“天道”精义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达,以开示考生。王阳明借助《易经》对“天道”观的阐发,亦是对朱熹“天理”观的发挥。王阳明对“天道”观的表述是十分严谨的,以此启发考生欲达“大人”之境界,就必须深悟儒家经典与“天道”之间的内在关系,明觉“大人”在开显、表述“天道”中的主宰作用,这一思想与王阳明其后所论证的“万物一体”思想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王阳明看来,绝不能把“为学成圣”与“存天理,灭人欲”两者对立起来,甚至当作两件事加以支离。在此文末,王阳明还用反问句作结:“大人与天,其可以二视之哉?”其结论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显然,王阳明对借《易经》阐发“先天”与“后天”的认识,源于儒家的天道观念,但王阳明在程式文中大大深化了这一思想,别出心裁,发人之所未发。王阳明将“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内在关系做了综合的判断,并将这一思想引入道德世界,化奥义为简明,体现了王阳明天道思想的简切明达。王阳明的天道思想,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不同意人为地割裂“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内在联系、以及反对将“天理”绝对化。正因为世儒对各种名利、欲望的渴求,人欲泛滥,最后导致人们发现“天道”的能力被弱化,心体被遮蔽,如此就很难开显出合乎天道的道德境界。王阳明还根据《易经》,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命题,通过河图、洛书与八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万物统一的“天道”问题,揭示“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同一性,这与朱熹的“天理”观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的,其共同点是都将“天理”或称之为“道”,指向道德意义世界。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在乡试程式文中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朱熹的“天理”观,两者之间是可以贯通的。相对来说,“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在理论形式上表现更具外在性与现实性,王阳明传承了这一思想,但主要侧重点在“天道”与“大人之道”的贯通方面,而不是着眼于具体的微观层面而已。
四、朱熹“诚意”学说对王阳明“修身”观的影响
“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炼要求,也是“立志”进德的自律途径,是《大学》中所列“八条目”之一。汉唐以来的儒学主要以训释经典为治学门径,对“修身”之道的学理探究则不太重视。到了宋代,理学家们不光继承了汉儒对经典训释的传统,还特别注重对先圣经典中关于“修身”义理的诠释,并引入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身之路。
朱熹在治学与教育方法上,要求学子直接面对经典而导入生命的过程,以回应社会所关注的伦理道德秩序问题,尤其强调人伦纲常需落实在生活细节中。朱熹认为:“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13]此言,揭示了“修身”是内敛的功夫,以“正心”为导向。重点在日常人际关系中加以自律,在言行上加以审察,及时改过,而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主要功夫,以“修身”为本。就方式而言,在言谈举止上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及情感的表达,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朱熹认为:“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14]朱熹的这一修身思想与王阳明的“修身”观内涵互补,相辅相成,只不过王阳明在表述上更加缜密,发挥更具神采。
立志修身,是王阳明道德修炼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思想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进入仕途后,省察自悟,学问思辨,在修身实践上深有所得,并将这种体悟作为引领学子“修身”观的价值理想。诸如,其在任山东乡试主考时,在试题中将“修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考察考生。王阳明据《中庸》出题:“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在程文中,王阳明阐述了修身的关键在于“尽持敬之功”。指出“九经”之本在于“修身”,又将修身分为“内修”与“外修”之统一,并以“孔子告哀公之问政”一事借题发挥:
“九经”莫重于修身,修身惟在于主敬。诚使内志静专,而罔有错杂之私,中心明洁,而不以人欲自蔽,则内极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严;垂绅正笏,而俨然威仪之整肃,则外极其检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复礼,而所行皆中夫节。不但存之静也,遏人欲于方萌,而所由不睽于礼,尤必察之于动也,是则所谓尽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以修身哉?诚以不一其内,则无以制其外;不齐其外,则无以养其中,修身之道未备也。静而不存,固无以立其本;动而不察,又无以胜其私,修身之道未尽也。今焉,制其精一于内,而极其检束于外,则是内外交养,而身无不修矣。行必以礼,而不戾其所存;动必以正,所而不失其所养,则是动静不违,而身无不修矣。是则所谓端“九经”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于持敬哉?大抵“九经”之序,以身为本;而圣学之要,以敬为先,能修身以敬,则笃恭而天下平矣。[15]
上述,王阳明将“内修”定义为“主敬”,而“主敬”则是“内志静专”“中心明洁”,将“外修”与“内修”联系起来。又将“外修”定义为:“穆然容止之端严”“俨然威仪之整肃”,认为人的仪容仪表“端庄”有“克己复礼”之约束力;而“内修”则为不以人欲自蔽。内外统一,动静结合,即能存静遏欲,合乎于礼。修身之道,以身为本,以敬为先,以实现天下太平、和合社会之理想。王阳明还将修身与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较透彻的论证。考其思想源头,是对《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思想的回应,这与《大学》要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完全一致的。修身的关键在于立志,这也是王阳明人生态度和思想探索的重要方面。王阳明还在山东乡试策问中据《中庸》出:“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诸君皆志伊学颜者,请遂以二君之事质之。”在程式文中,王阳明将古代圣贤伊尹之志和颜子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阐明了人生的境界是“箪瓢之乐”:
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能穷理,故能择乎中庸,而复理以为仁;能慎独,故能克己不贰过,而至于三月不违。盖其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宽体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后能知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也,然后能知颜子之学。生亦何能与于此哉?顾其平日亦在所不敢自暴自弃,而心融神会之余,似亦微有所见。[16]
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的“慎独”。只有通过内心的修养,才能达到内圣,只有做到内圣,方能够治国安邦,达到外王的目的。因此,王阳明十分推崇孔门弟子颜回的“内圣”精神,自我主宰,独立独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同时,王阳明也十分敬仰商初大臣伊尹的才德。告诫学子,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都要以修身养德为要,内具圣道,外施王道,师范天下。王阳明将伊尹之志和颜子之学作为自身道德修炼的楷模,体现了道德观与政治观的统一,“修己”与“治国”的结合,体现了《大学》三纲领的基本要求。相对而言,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王阳明不仅推崇“箪瓢之乐”的人生境界;而且对伊尹“见细微于平常”的“修己”与“治国”相结合的“修身”进路同样赞赏,这是其“修身”思想探索的重要内容,更是其立身的准则。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在《题汤大行殿试策问下》中对“修身”思想的论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汤者数言,而终身践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数言,而终身践之。推其心也,君其志于伊、吕之事乎?夫辉荣其一时之遭际以夸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则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鉴也。昔人有恶形而恶鉴者,遇之则将掩袂却走。君将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乌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于伊、吕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17]
在上述题辞中,王阳明十分强调为官者当有“伊、吕”之志,必须做到“言行一致”“以言为鉴”,即以自己所言对照自己所行,摒弃那种口是心非,知行二分的“伪君子”行径。可见,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程式文中对“修身”的阐述,与朱熹的“修身观”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程式文中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发挥而己。在修身学说上,朱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逻辑性的哲学范畴,构建了一套严密的道德本体论、认识论和工夫论体系,代表性的学说是“格物论”,即“格物穷理”。尽管“格物论”的逻辑外延十分宏阔,但其中自然包含了儒家的修身之论。王阳明年轻时,因深受朱熹修身”诚意”观的影响,在自身道德修炼中虽有不少困惑,但总体上对朱熹的修身观是接纳、融通的。
结语
综上言之,对王阳明前期思想发展进路的考察,朱熹理学对王阳明心路历程的影响十分密切,这为其“阳明心学”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若离开这一发展阶段也无法说清楚“阳明心学”产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是前后联系的。从对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深入探究中,可以明显发现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在诸多方面是深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的,这可为深入研究阳明学提供某些方向性、前瞻性和基础性的学术视角。同时,通过探究王阳明前期的思想发展进路也可反观朱熹思想的丰富性、独特性,为世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观察点。阳明心学是在对朱学的发明、碰撞中逐步开新出来的,尤其是对朱熹“格物”学说的辩证,是阳明心学生发的一个切入点。在王阳明的那个时代,无论是信奉程朱理学还是信奉陆王心学的学人,一般来说,都具有包容的心态,亦师亦友,相互辩难,即使学术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但私谊如故。可以说,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中一直伴随着对朱熹学说的接受与质疑、批评与开新,方成其大。阳明心学的发生是因朱熹的“格物”学说而起,朱熹学说作为潜在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范式,从方方面面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两者的融通,无论对研究朱熹理学还是研究阳明心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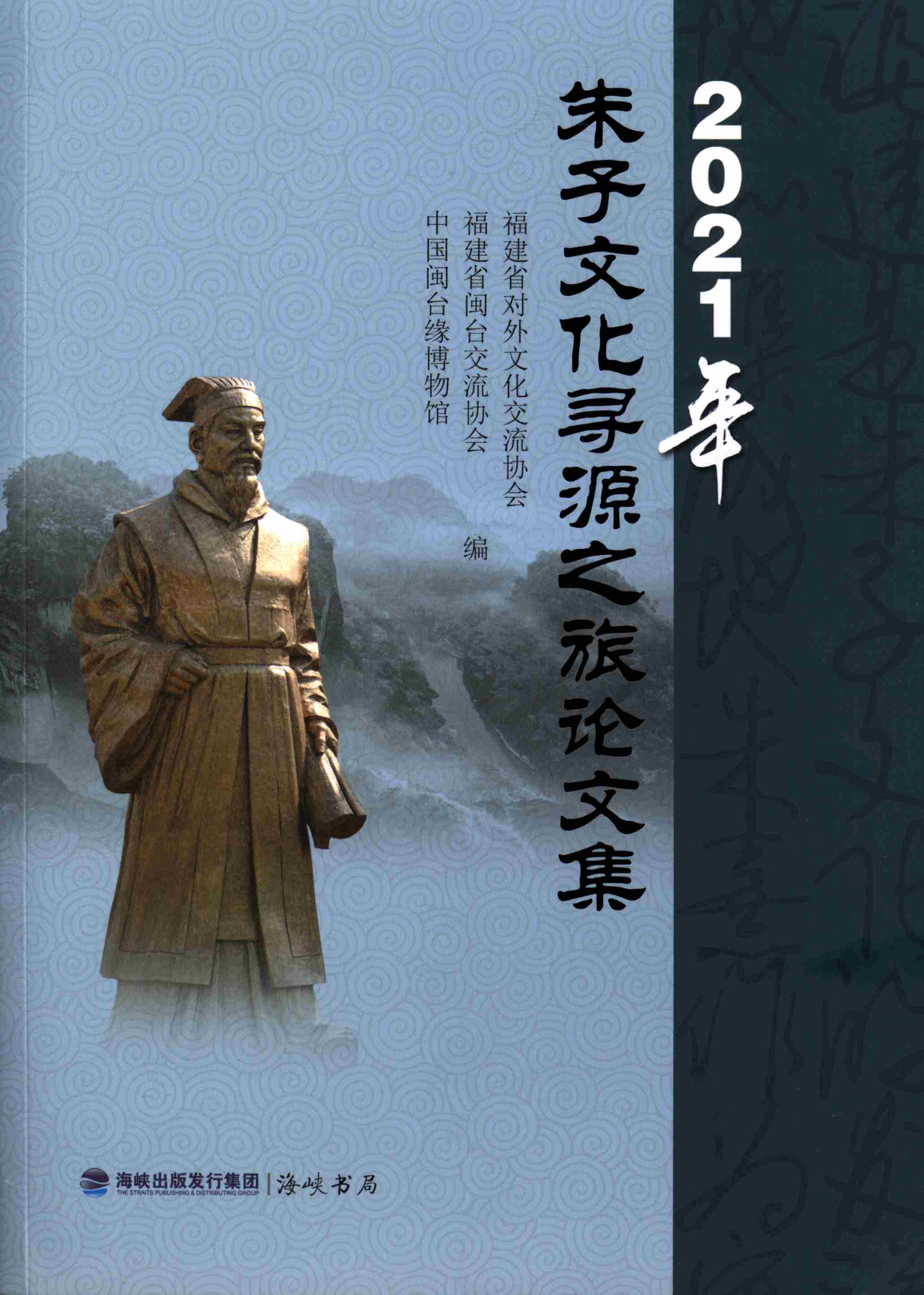
《2021年朱子文化寻源之旅论文集》
出版者:海峡书局
本书收录了《展现福建传承弘扬朱子文化新气象》《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朱熹的民本思想》《武夷山朱子文化旅游价值与建设路径》《民本视域下的朱子慈善思想及其实践》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