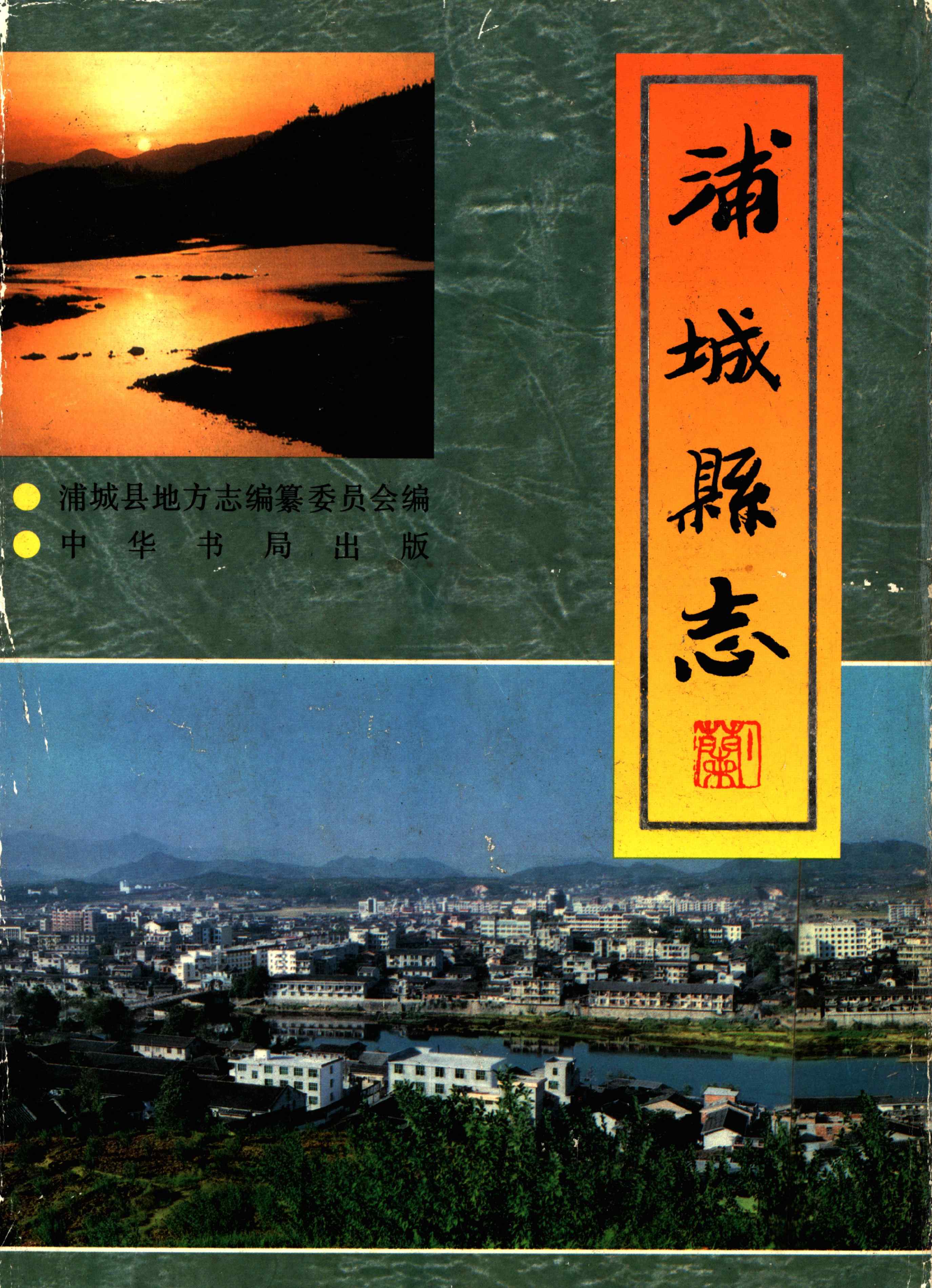内容
杉坊花鸟志 郭风
题记
七十年代初期,举家四口旅居于闽北浦城县的一个小山村。村名下杉坊。连同我家,这个自然村当时只住四户人家。就当时的乡村行政体制而言,它隶属于九牧公社的杉坊大队。而此大队又辖九个生产队,共有二十个自然村。
最远的一个生产队,离下杉坊村约十华里,它在著名的渔梁岭上。那里,至今还能见到古驿路和寨门;从蔡襄等有关的诗文中可知渔梁驿至少在宋代已是一座繁华的山镇。全大队都在海拔八百至九百米的深山重岭之间,有三条山溪流经境内,其中有二条山溪便在我当时的居屋的门前汇合,出山口流入江西。溪流上有木桥,溪畔有水磨坊,林木蓊郁,鲜花遍野,鸟声时或传来。大约在1984年间,曾作一组散文,题曰《杉坊花木志》(收入拙著《给爱花的人》,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作《杉坊花鸟志》,除记述我在杉坊的所见的花木、禽鸟外,也将记述我对于那里的鱼、虫以及小山兽等的印象和感受。或可作为他日收地方志(譬如《浦城县志》)者的参考。
果子狸·夜雁
记得是1971年11月中旬来到杉坊的。先宿浦城城关一夜。竟夜大雨滂沱。次晨雨止,驱车至九牧公社报到,只见办公室内,中央置一火盆,盆内炭火融融,几位干部围在火盆边学习文件。他们见我一家人来,都让坐,且说山岭上已经下雪。
我在杉坊住下后,记得从秋暮到冬天,下过几场大小雪。若在晴日,则往往下霜或结冰。秋收以后,村里的梯田,除了一部分种上荞麦和紫云英的以外,皆裸露着,上面结着薄冰。至于霜,每在结冰之前的晴朗的深夜里下降。一天下午,我作为当时的所谓“下放干部”,参加大队党支部所召开的各生产队队长会议,内容主要是落实次年的春耕生产的种子、肥料等的分配问题。我不记得是什么缘故,直到将近半夜才结束(大家在大队部吃晚饭)。会后,我与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自然村的老王同行,一起回家。老王四十开外,满腮胡髭,山间天冷,但见他只穿一件到处补钉的旧棉衣,腰间束一条腰带,那旱烟管斜插在腰带里,却又不时取出,吸它几锅。且说这天夜间,我们从大队部出来,向下杉坊村里走去,一路上只见田埂上、篱笆上、村屋上、枯叶尽脱的乌桕的树枝上以及那些稻草垛上,一一凝上白霜。霜夜的月色格外清明。老王在全大队是爱说笑话和编造趣闻而出名的,记得那夜在月光中冒着彻骨的寒气,在村路上边走边听他讲些趣闻,忽然,他停下话,按着我的肩膀,要我和他一起蹲下来,说:
“瞧!——”
我蹲下来,向路边不远处的一座稻草垛望去,只见垛堆间有一只小山兽喷着鼻息,两只绿宝石一般的眼瞳里发出亮光;它似乎在警惕什么,似乎在思考怎么逃脱,似乎在估量目前有什么危险……
只见老王蹲在我的后面,从腰间抽出旱烟管,在地上敲着,好像小孩子那样,笑嘻嘻地:
“别怕,别怕,你尽管躲着——”
只见那小山兽却从稻草垛里闯出来,箭一般地从路边跳上附近的田埂路,一路踏着浓霜,往一片树林里躲进去。在月光下,我看见这只小山兽好似一只山猫,但体长,眼边有白色条纹。老王扶着我站起来,笑笑说:
“别管它了——等下它还会回来,躲进稻草垛里——”
他告诉我,这小山兽当地人叫它笑面狸(我查了辞典,得知学名为果子狸)。霜天,山上更冷,这小山兽便跑到村里,躲在稻草垛里取暖。据老王说,笑面狸跑到稻草垛里,有时也为了寻觅未打干净的稻穗上剩下的谷子。但它主要是吃山上野生的山楂呵、杨梅呵、野李呵。老王还对我说:
“这小家伙还会吃小鸟呢,哈!哈!”
他说,有一次在林中找蘑菇,不意树上的鸟窝里掉下一只雏鸟,没想一只笑面狸从林间跳出来,把雏鸟啣在口里,就往树林深处跑去……
记得又有一次,也是下霜的深夜,开会后,老王陪我从大队部回到我家(他总是送我到家,然后自己回去)。他在我家门口的石阶上站住,望着澄蓝的夜空,忽然说:
“你看——天上有雁阵……”
我抬头一望,真的看到在北斗星座的斗柄下,有排成人字形的雁阵自北往南飞行,我好似还听得有“咯咯”的雁鸣声,自远天传来……
老王说:
“它们从苏武牧羊的地方飞来,已飞过开封府、苏州府,正向延平府飞去,最后飞向兴化府、泉州府的海滩上去过冬……它们飞过的路远啦,嘻嘻哈!”
不知怎的,那夜久久不能入眠。心里一直在想,儿时也曾在家乡莆田(即老王所说的兴化府所在)的秋空中,看到雁阵,但感那样的岁月离我已很遥远,一如秋雁的旅途!
小麂·刺猬
那天夜里,村里下了一场可能是入冬以来最大的雪。山中有一段冬闲的日子,天又冷,这样,村民们往往在天暗后不久便闭户就睡。这场雪大约就在这时候开始纷纷飘落,可能直到夜深才止。就我自己而言,可能是所见最大的一次雪。记得当时我所居住的下杉坊村,只见四面的山峦都盖上白雪;村屋前不远处的木桥盖上白雪,溪中的岩石盖上白雪,溪边的水磨坊和一座土地庙,以及田埂路、还有晒谷场都铺满了雪;我和邻居的屋顶上更是盖着厚厚的雪,而且,早晨起来时,屋前的石阶都给雪封住了。这样的雪天,山上的雪必定下得更大,有一些小山兽便跑到村里来,寻找取暖的处所。
有一只小山麂就从山上的密林里跑下来,躲在我当时的邻居阿方伯家灶间的干草堆后面。根据一点迹象,我估计这只小山麂对于山中大雪之欲来、将降,有一种本能的预感,而且会本能地去寻找可以躲藏之所,记得当时我竟会作这样的“判断”,以为这只小山麂是在大雪下降之前,便跑到山下村里来;而且又是在阿方伯一家闭户就睡之前,便悄悄地走入灶间里的,它在干草堆后面安安稳稳地躲藏(取暖和睡觉?)了一个整夜。
记得那天得知阿方伯家里跑来一只小山麂,我立时走来看望这只小山兽。只见阿方嫂坐在灶下,边用刈稻刀切着干草,边喂着那只躺在她身旁的小山麂;只见它卟哧卟哧地喷着鼻息,好像感到十分可口地嚼着干草。我似乎还是初次见到一只小野兽和人能够处得这么亲近;并且,当我走近它时,它似乎也不感到陌生和畏惧……
我不觉随口说了一句:
“何不如把这只小山麂养下来……”
听了我的话,站在一边尽是吸着旱烟管的阿方伯,笑笑道:
“还是要把它放回山上去的!——”
我仔细地观察一下这只小山兽,感到它有点像鹿,但体形比平日在动物园里所见的梅花鹿小得多;其毛,背呈棕褐色,腹呈白色,油润而光滑。我感到它很可爱。却见阿方伯抚着它的头,又笑笑说:
“你看,它头上无角,是只雌的——放它归山,可以传子传孙,哈哈哈!”
在整个杉坊大队,这位年约五十余岁的农民阿方伯,都受到尊敬。有人说他能知天文,说他看星、看云、看天色,能知若干天内的气象。他还熟悉当地的水利以及传闻轶事和民俗。有空时我喜欢和他闲谈,感到他的随意谈吐间,常常出现一种山地农民的幽默感,又含有某种朴素的民间深意。那天,他还告诉我,按照村里自古以来传下的习俗,凡山上有小兽躲到屋内来,不论是为逃避猛兽的追逐而来,还是为逃避某些祸害(譬如山中风雪等)而来,均不得杀害,且要挂红送回山上……
这只小山麂被养在阿方伯家两天两夜。阿方嫂每天给它喂谷物、干草。第三天,雪开始消融了,早上便出了太阳。阿方伯找到一方红布,系在小山麂的耳朵上,自己怀抱着,准备放在村里的土地庙前,然后让它跑过山上的密林中去。下杉坊村的一些村民,包括我这位“下放干部”,都陪同他一起给小山麂“送行”。我们走过木桥,走过长长的一段溪边的小径,正走近水磨坊时,阿方伯忽然停下脚步,他似乎听见水磨坊内仿佛有什么动静……——原来是一只刺猬躲在水磨坊的小房里面;它大概听见人声(以及人的气息?),下定决心从里面冲出来;只见它喷着鼻息,隆起全身的针刺,像突围似地冲出来,几箭步便冲在土地庙前,然后沿着被融化的雪水浸蚀的小泥路向密林中逃去……
对那逃荒似的刺猬的背影,阿方伯笑笑说:
“别慌,别慌——只要你不偷走地里的番薯,不会抓你的……”
有人在水磨坊的小房里看一下,只见地上有一大堆灰烬,是舂米的村民烧木炭取暖时留下的灰烬。这只刺猬大约便躺在这灰烬上度过寒冷的积雪的夜晚?
再说大家跟着阿方伯把小山麂送到土地庙前后,便放它自己往山上的密林中跑去。却见这只小山麂真像有心人一样,跑了几步,便站住回头看看大家——最后才跑进林中,不见了。记得在杉坊时,我有时感到某些小山兽能察人意,能与人亲近;有些小山兽,对人则永远保持距离,永远对人保持警惕。
杜鹃花·虾·竹鸡
多次想到西源垅去走一趟,好好地看一看,但总被别的事耽搁了。西源垅是杉坊大队的一个狭长的山垅(沟),有一条山溪从这里的山间流出来。想到西源垅看看,有若干原因,譬如很想实地观察那里的自然环境以及到独户住在那里的老杨家里去坐一坐,等等。老杨本人曾多次约我到他家里看看,这中间更仿佛出现某种需要履约的情分,使我难以忘怀。记得是清明节后的某一天上午,我一人沿着溪岸陡坡上的小径,随意漫行,且看,且在笔记上写下一点记录,有时便坐下休息,准备在午饭前来到老杨家里。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开放的杜鹃花,自是在杉坊大队这一带地域内。从我当时居住的下杉坊村,南至渔梁岭,北至九牧公社,遍山遍坡,一座山峦联着一座山峦,视线所及,我觉得满目都是血红色的杜鹃。有一次我到九牧公社去开会,途中曾见到若干山岩上只要有一点泥土,便会长出小棵的杜鹃,并开放血红的花朵。据我现在的回忆,整个花期长达二十余天。不过,据当地群众所称,杜鹃花开放得最旺的还是西源垅一带。那天,我一进入西源垅,便见从山口开始,沿溪的山坡上全是杜鹃花。其间,我很快发现,而且全是一种灌木,有的甚至高达五、六丈,花形看来也较为硕大。最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在满山灿烂的血红的花朵中间,见到有的杜鹃开放的却是雪白或桃色的花朵;更见到在杜鹃树下,金银花也在开放花朵。
记得那天我是沿着溪流北岸的斜坡深入西源垅里。在垅内行了大约三华里,岸边出现一片开阔地。不知怎的这开阔地长着矮矮的、褐色的不知名的小草,无树木。远远地,我便望见那天阔的草地上有一群斑鸠在觅食草籽,它们咕咕地叫,至少有二百余只。这又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一群斑鸠。和我小时在家乡莆田所见的斑鸠相比,它们体形较小,颈部的羽毛呈灰蓝色,很有光泽。当我走近时,它们也不高飞远走,只是各自转身向四面稍为分散飞开;待我稍为走远,——我回头一看,它们又都飞回草地上觅食,并且咕咕地叫。我心里想,这大群的山斑鸠,好似知道我是不会损害它们的;但当时我又想,这是一群警惕性不高的山禽?记得离这片草地大约又二华里,有一道用三根树干拼成的木桥,从岸上搭到溪中的一堆大岩石上。过此桥,便走向南岸。桥下溪水汩汩,激着错列的溪石,溅起水花。不知怎的,当时忽生一奇怪念头,即想蹲在桥上观察溪中的“动态”。有趣的是,居然见到一只溪虾。它全身呈一种透明的灰绿色,长约八厘米,头上有很长的触须;我见它一动不动地停在水中一块平滑的溪石上,有时稍稍地动一动触须。我至今还想不出来,这只虾何以一直静静地停在那里?
溪的南岸有一些梯田,村民称之曰“山垅田”。这山垅田原来只宜于种单季稻,但当时有关方面,却强制推行双季稻的种植,虽然有不同意见,但被用“保守思想”的帽子压下来。这样,自古以来不种双季稻的山垅田,这时节也种下秧苗,并且正在发青。一路上,我想着老杨当时曾因对在山垅里种双季稻,在思想上不通受过批评。但村民们却因此更看重他……我边想边走,沿着山路向老杨家里走去.不想,我过桥后才走了一段路,老杨和他的一只纯乌毛的猎犬,便从前方向迎我而来了。像村里的一些中年农民,老杨也满脸胡髭,吸旱烟管。我初到杉坊时,便听人说过,老杨一对公婆独户住在西源垅,主要是为便于打野猪,好保护山垅里大片梯田的收获。又听说,老杨枪法虽好,但只打野猪,山上一禽一兽,全不损害。甚至有人说,山垅里的有些野禽野兽还和老杨交成朋友呢。记得那天到他家里,只见屋后山上种了一片杉木林,又种一片竹林,都管理得很好。家里还养了三、四只鹅,一见我来,便咯咯地冲上来,好似要咬我的腿。老杨说:
“山上有蛇,养了鹅,蛇不敢来了——”
据老杨说,鹅吃的全是山上的草,其中有的草能治蛇毒,且为蛇所畏惧,鹅粪中含有这种草的渣,蛇一见到(嗅到?),便不敢来……
那天,老杨留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喝清明前刚焙的新茶。这午饭真别饶趣味,除干饭外,汤都是用临时在门前的水沟里抓来的泥鳅、黄鳝等做的。午饭间,老杨忽然站起来,向灶堂外面的竹林里,呼鸡一般地唤着,却见从竹林中走出一群竹鸡;它们有鹧鸪那么大,全身是褐色的羽毛;它们咯咯地叫着,争吃着老杨抛去的饭团……
后来我知道,老杨在早上或午间用谷物或午饭喂养竹林中的竹鸡。说也有趣,时日一久,这些山禽一听老杨的呼唤声,便从林中跑出来了,好像家禽一样。我有时想,这位老杨不仅是农民,更是一位对于山禽山兽怀有某种特殊感情的猎人。
飞雪的春节 何为
又是飞雪迎春的时节了。
那一年,我的家在山林深处。村屋依傍着山岗岩壁。大门外,奇幻多姿的武夷山脉鹫峰支脉举目可见。院子前有一棵百年大樟树,盘根错节的老树下,环抱着一口古井。这里是山区农民到浮桥小镇去的一条必经之路。往来的过路人往往在浓荫覆地的水井旁歇脚休憩。
我的家属于这个小山村的第二十七户。前边围着高高的棕色土墙,墙内重重院落把各家连在一起,俨然自成一个山寨。据老人说,多年以前,一个来自外省的卢姓拓荒者,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脚下披荆斩棘开辟一块耕地。过了几代人,逐渐形成一个自己的村落。又因为地处溪滩的拐弯处,就相沿称之为卢家湾。
我们刚搬到时,颇惊异这陌生山乡的熟悉地名。卢家湾这个地名,有如从记忆深处迸出的一声回音,骤然唤起我在上海漫长岁月里的无尽思念。那个大城市也有卢家湾。那时候全国城乡都蒙受苦难,我有一种奇异的乡愁。
经过大风暴初期的动乱日子以后,我终于被放逐到这样一个僻远的山乡,来参加劳动,而且终于在这里安了家,实在是一种当年难以祈求的“幸福”。回想在那些灾难的岁月里,不知多少人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同我住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下放干部就是我的妻子,还有在身边的女儿。我们一家三口享有一个有灶头的厨房。旁边一间土屋当作寝室。正屋有一耳房是一间朝南小屋,厚实的土墙上半截,横列着一排整齐的木档。我们取一块卷铺盖的塑料薄膜把宽阔的窗户严严遮住,既可聊蔽风雨,又可照入阳光,成为极富有装饰意味的窗棂。这间在山村里少有的明亮土屋,我们用来兼作卧室和书房,也是接待左右邻居的所在。
那时,我们都喜欢这个远离尘嚣的僻静的农村之家。我的妻子下乡时,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农村医疗手册,自己又置备了一些常用药物,以防不时之需。一次,沉默寡言的老生产队长站在门槛边半天不说话,一看才知道他出工不慎踩着竹尖,脚底全是血污,当即给他作了消毒处理,并用纱布包扎了一下。又一次,房东大娘的孙女儿芳婷患感冒发烧,量过体温,配了一些扑热息痛及长效磺胺之类交给他们。以后不断有人上门来索取一点药,或者要求涂点消炎药膏,我们这间小屋竟又成为简易的医疗室。
那些整年累月在山地默默劳作的农民们,平时为了买一斤粗盐的钱都得到处张罗,轻易是不愿到七里地的小镇卫生院看病的。开头几天,他们多半很拘束地侧立门旁,难得跨进我们的小屋。但是数月后,除了生产队干部带到这屋内研究队里的工作以外,就有一些大婶大嫂带着孩子找上门来,高高兴兴地坐在屋里闲话家常了。在我们自制的小油灯火光摇曳下,经常是一壁厢笑语人声,一屋子人影晃动。
不久就临近春节。过了阴历十二月半,生产队里的年终分配大抵已接近尾声。人们胼手胝足劳动了整整一年,现在家家户户开始蒸年糕,酿米酒,炒花生,做芝麻糖等等。那怕仅仅是一种节日的点缀,一种传统年景的象征。这个生产队历来种籽瓜,以瓜子颗粒大而饱满闻名远近。在柴火哔剥的大灶头上,热铁锅里炒瓜子的声音,是多么富有魅力,谁听了都会感受到过年的欢乐气氛。
山区的冬天严寒逼人。我们的小土屋里,烧着一盆炽热的炭火。火光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作玻璃的木槅窗。窗外是一角灰蒙蒙的欲雪景色。已经是岁暮年边,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那两个在少年时代就过早地离开学校,到另一处山区去插队劳动的男孩,不是来信说回家欢度春节吗?做母亲的不知多少次站在大樟树下举首翘盼。她心神不宁地刚刚回到灶头旁,忽然小女儿雀跃地大声欢呼起来,向外飞奔。在微雪的幽明中,两个肩挑重担的少年推开了自己的家门,把他们这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收获都挑回家来,回到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家里。
这在小山村也是一件新闻。许多相熟的农村妇女纷纷进门来探视,看看下放干部全家团聚的情景。心地忠厚的房东大娘,从我们住在她家里的第一天起,便处处关心我们。她大约六十多岁,终日忙个不停,善于在不同节日里做各种美味的农村传统食品,以她的巧手和为人热诚,受到全村的尊敬。她正在热气腾腾的蒸笼旁,忙着帮我们家做红糖年糕,这时一转身从她的住屋里捧出一大包炒花生,非要塞到我的两个儿子手里不可。过了一会,老队长特意拿来一瓶家酿的桂花米酒,默然无语就悄悄离去了。随着邻居们亲切的问询,不断送来油麻糕、寸金糖和糯米团,各种各样家制的糖食和糕点。啊,善良的、纯朴的、可亲的山区农民们,你们送来岂止是最好的节日食物,还有一片使人为之感动的真切情意。
大年夜落了一场瑞雪。繁密的雪花闪闪烁烁地漫天飞舞,整个山村笼罩在沉静的飞雪之中。在这仿佛与世隔绝的山乡,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年饭,随后一家人围住满盆炭火。火盆上的水壶冒着热气的氤氲,伴随着沸水欢乐的嘶嘶作响。红烛初燃,笑语盈室。真的,我们记不起那一年的除夕比今夜更温暖了。
然而,在这飘雪的岁末之夜,在远离我们小屋以外的全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有多少团聚的家庭,又有多少离散的家庭?多少人有家归不得?多少人无家可归?我们凝视着明亮的炭火,怀念失去音讯的亲友故旧,默默祝愿他们都能欢度这新春佳节,愿祖国大地上的人民在未来的每一个春节都吉祥如意。
大年初一的清早是在爆竹的脆响声中醒来的。睁眼一看,呀,整个小土屋都是银亮的雪光,横窗上嵌着白色花纹似的雪花,屋檐凝结着白珊瑚般的冰串。我们迫不及待地推开小院的大门,门外是一个广漠的白雪世界,白得宁静,白得肃穆。真想去拥抱这洁白的大地。一股清冷的新鲜空气迎面扑来,不知怎么想起学生时代喜欢的惠特漫一句诗:
“啊,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
这个年初一的雪朝,我们在满头皆白的大樟树下走过。遥望溪流对岸,白皑皑的群山屏立,象一幅银灰色调的庄严版画。踏着雪,走到溪边渡口去的曲径小道,厚厚的积雪印上我们一家人蜿蜒的足迹。渡口那棵满是冰雪的大树上花开满枝,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一树迎着严寒来报春的是梅花!
山林深处的卢家湾,别来无恙否?你在我们最感到孤零的时候给我们温暖,你在我们最寂寞的春节中带给我们最难以忘怀的节日愉快。你是我的第三个故乡,还是第四个故乡?也许有一天,我将在那个大城市里的卢家湾想起你。我一定会想念你的,在每一个飞雪迎春的日子里。
故乡的梦 季仲
我的摇篮
从崇山峻岭中的汩汩淙淙地走到平原上来的南浦溪,是我幼年的摇篮。
那潺潺的溪水,明净如水晶,莹洁如碧玉,温柔得象母亲贮满了爱的眼睛。
夹岸的桃花、垂柳以及生机勃勃的芦苇、马鞭草和箭竹林,为我的摇篮装饰着织锦一般的花边。
蓝天、白云、朝霞、暮霭以及雨后初霁横贯长空的七彩长虹,常常装满了我的摇篮,变幻出一个无限辽阔而神奇的童话世界,引起我这个小傻瓜多少天真、高远的遐想呀!
我曾和我的穿开裆裤的小伙伴们,在溪流里学会“狗爬式”;
我曾跟随老渔翁驾一叶竹筏,停在江心看鹭鸶叼起欢蹦乱跳的大鱼;
我曾拽着水牛的尾巴,闯过急流飞湍的漩涡。
溪滩上,夏夜蟋蟀们的鸣叫,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优美的奏鸣曲;
溪埠头,朝霞辉映下的浣衣女,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动人的水彩画;
而那风雨如晦的沉沉黑夜,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农妇跳溪自尽的悲剧,则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启蒙课。
呵,亲爱的南浦溪,你琼浆玉液般的乳汁哺育着我。整个孩童时代,我在你的怀抱里作过多少次温馨的梦!
呵,亲爱的南浦溪,你母亲一般的爱是深沉的、博大的,你养育了你的儿子,却不会娇宠你的儿子,让他蜗居于一个小小的天地。儿子长大了,你掀起你透明的风,扬起我年轻的帆,沿着蜿蜒曲折的航道,穿山越谷,击水南下,驶入闽江,停泊在一个书写着我们民族的光荣与耻辱的海口。
于是,我见到了碧波万顷的茫茫大海,见到一个辽阔恢弘的大千世界。
然而,南浦溪呵,我童年的摇篮!至今我仍常在梦中,听见你的溪滩上的蟋蟀的吟唱,看见你的清流上那流萤一般的渔火一闪一闪。
山中的海
我是山的儿子。
我外婆家在很高很高的高山上。那里满山遍野都是翠生生的毛竹。
小时候,我没见过海。但在我的想象中,这无边无际的毛竹林,不就是绿色的海——山中的海吗?风和日丽的日子,凤羽状的竹枝竹梢,纹丝不动,竹林里悄无声息,静得象深不可测的海底。
风狂雨骤的日子,每根毛竹都被刮得前伏后仰,发出惊涛骇浪的唿啸,显示出大海的粗犷而雄伟的气魄!
我记得,我曾和我的小伙伴们在竹林里拖过毛竹,挖过冬笋。我还记得,用笋壳的小尖儿做成的小笛子,能吹出一种迷人的、温馨的、带着乡土气息的曲调。
我记得,我外婆村里的舅舅姨姨们都是能工巧匠。他们一拿起平平常常的篾刀,就都变成神通广大的魔术师。纤细如发、柔软似绸的篾丝,从他们手下流出来,流出来,在地上浮起一片带着清香的云彩。他们编织的花篮,象花一样,散发着芬芳的气息;他们制作的鸟笼,即使没有画眉鸟儿,也会唱出许多醉人的歌。
呵,至今我的书案上还放着故乡青竹做的毛笔筒。每当看到它,我就深深地怀念那一片绿色的海,故乡的海,山中的海。
木偶大师
他是全才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大师。
在村寨的祠堂里,或小小的晒谷坪上,他和他的助手仅用四张八仙桌,或几块长木板,搭起一个小舞台,拉起一块绣着“天官赐福”的帷幕,就能撑起一个具有非凡艺术魅力的大剧院。
于是,他就能给淳朴善良的山民们带来历史和文化,带来神话和童话,带来诗和音乐,带来生活的欢欣、慰藉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能够扮演生、旦、净、末、丑所有行当。他还兼任着编剧和导演。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流动剧团。
在我的记忆里,他唱花木兰,赛过常香玉;他唱黑包公,赛过李少春;他掌中的三花脸儿,滑稽、诙谐、风趣、刁钻,集我生活中见到的可爱与可憎的人物种种妙处于一身,憨态可掬,美不可言,比起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也毫不逊色。
他那灵巧的五指牵动木偶们作出捋须,甩袖,骑马,挥鞭,舞剑,厮杀……等等动作,情态毕肖,栩栩如生,真不亚于一个造诣精湛的优秀演员。
我还没到上学年龄,就从他的表演中认识了孙悟空和猪八戒,梁山伯和祝英台;就记下了《三顾茅庐》和《林冲夜奔》等许多历史故事。
他那魔术师的手指和金属一般经久不衰的好嗓门,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智慧,把我带到一个多么奇妙的幻想世界!
啊,即使我在首都一流的艺术剧院欣赏过一流的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我还要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故乡的木偶戏,不会忘记那位全才的杰出的却名不见经传的表演艺术大师!
山城水清清 沈世豪
位于闽北山区的浦城,素有“小苏州”的美称。最令人留恋的,是城里的水。
浦城是山城,老城是沿着仙楼山而建的。小巷深深,夹巷一律是青灰色砖墙,又称风火墙。倚墙的庭院,很有气派,几进几出,最大的竟住了九十九户人家。清粼粼的南浦溪绕城滚滚流去,人们毫不足惜。因为,城里有井。最驰名的一口,叫清水井。以前,这里人喝水是很讲究的,只喝清水井里的水。这口井在老城正中,又称学前,那水清冽冽的。城里人待客、迎客的不是茶,而是泡一杯糖桂花。杯子是无色玻璃的,滚烫的水刷地冲下去,桂花瞬间全开了,鲜灵灵的和活着的一模一样。主人笑盈盈地递过一支花瓣状的长柄小银匙,轻轻一搅,红艳艳的桂花开得生意盎然,扑鼻的清香,丝丝缕缕,浓浓淡淡,悠忽沁人心胸,又悄然弥漫开去。品一口,余味无穷,仿佛消融在一派氤氲的香韵里。这都是因为清水井的水好。不信,你试用南浦溪水泡泡看,不仅桂花不鲜,而且还有一股水腥味哩!
城里新建的高楼,以及颇有气派的机关大院,是不乏自来水的。全县虽设有自来水公司,许多单位都备有抽水设备,但人们还是喜欢喝清水井的水。每当早晨,或是傍晚,到清水井挑水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窄窄的老街,铺着麻石,两旁是斑斑驳驳的木骑楼。挑水的人多了,水溢出来,濡湿了街道,乍看去,潮润润的,既觉得故里的温馨和亲切,又觉得古城淡淡的悠远和闲适。远走异国他乡的山城人,恋情绵绵不绝,这街道,仿佛铺在游子们心灵的深处。清水井也奇,无论多少人挑,从来没有干涸过,终年水清,纤尘不染,更不消说有一粒泥沙了。因而,也不必“洗井”。人世沧桑,这清水井,总是那么坦坦荡荡、盈盈的,仿佛藏着一个迷人的秘密。
闽北的山城多,数浦城文气重。历代人材辈出,状元且不去数它,仅在宋朝,就出了八个宰相。城内的孔庙,巍峨壮丽,金碧辉煌,不仅在闽中首屈一指,而且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数米高的孔子塑像,温文尔雅,栩栩如生,塑像的泥土,取自数千里之外的孔子故梓曲阜。不幸的是,“文革”中的一炬,声名显赫的孔庙竟夷为平地。人常说,地灵人杰,山城的老年人爱谈古,免不了论论风水阴阳。往往又牵扯到清水井,都说是这水养人。我不信,曾和一位远房亲戚论过。
“你不信么?”他用眼睛乜斜着我。愤懑、鄙夷,甚至有点动怒了。仿佛我是一个背叛列祖列宗的逆子。
“你细细地看看,这清水井养出来的姑娘都特别漂亮。”他忽然又找到了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我们一齐笑了,这可是真的。浦城的姑娘长得美,肤色好,水灵灵的,洁如凝脂。高高的身量,婷婷娉娉,素雅高洁,象绿竹青青,象涧水潺潺,别有一番迷人的韵致。浦城话也好听,柔媚而不乏刚健,细软而又不嗲声嗲气,既有吴越方言的甜润,又含闽粤客家的质朴。尤其是女声,更是动人三分。浦城姑娘爽朗,如五月的武夷山,眉清目秀,而不象深居闺阁的淑女,羞羞涩涩,她们爱美,并不着意在衣饰上精心打扮,而是善于用自己的巧手,描绘明明净净的山水画。人爱清水井,那清粼粼的水,莫非亦钟情于山城的灵秀么!
少年时代,常去清水井挑水。井台高,井深不见底,只看到井壁内厚厚的青苔。汲水是极有功夫的,因为看不见井里的水,只凭手中吊桶上绳子触觉。汲水的吊桶放下去,放下去,蓦地,从水井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呼地一声响,手中的绳子也仿佛失去了重量,只须轻轻一抖吊绳,约莫三、四秒钟,水便汲满了,麻利地将吊绳在手腕上缠上两圈,猛地吊上来,两手交叉地提呀提呀,扑面一股凉意,转眼就将水提将上来。颤悠悠地挑着一担玉露似的水,从熙熙攘攘的闹市穿行而过,自有几分快意。
也有孤寡人家,缺乏体力,便雇人去挑。若论担数,一担只须二三分钱,也有按月数的,价钱更是贱得很。我认识一个专以挑水为业的哑巴,人们不知他姓什么;只叫他“哑子”。他是汲水里手,只见他口中含着香烟,手中吊绳只一抖,腰也不弯,不出三秒钟,满满的一桶水便轻而易举地提将上来。偶而,逢到体弱的老人和小孩前来挑水,隔着几尺远,他头也不抬,把将上来的水,整桶倒过去,刷地掠起一匹弧形的银练,待你清醒过来的时候,一桶水滴水不溅地落在你的水桶里。人们往往带着嗔笑感激地说:
“这哑子——”
他是听不见的,仿佛不当一回事,手中的吊绳一抖,一桶水又汲上来了。我很赞叹他那一手绝技,更由衷地敬佩他那象水一样纯净无瑕的心。我曾到他家去玩。他最爱吃豆腐,平时,极少吃饭,往往是以豆腐当饭的。清水井水好,做出来的豆腐也特别鲜嫩,细心的哑巴,可能是真正品出味儿来了。
转眼一二十年,哑巴不知是否还在人世?远在异地,闲暇时节,也牵起淡淡的乡愁。浦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了,但清水井还在。山城水清清,汩汩,森森,点点滴滴在心头,更分外撩人思绪哩!
故里,捧出一盅木樨茶 祝文善
不管你去到多远的地方,不管你离别多久的时光,故里,总像一块巨大的无形的磁场,紧紧吸住游子拳拳之心。
谁也不曾想到,回故乡的路竟然走过多少岁月!海峡两岸的藩篱,隔不断血浓于水的乡情,一位又一位海外游子,一批又一批去台人员,终于回到生养自己的闽北浦城。不知为什么,品尝过法国白兰地、英国威士忌、日本清酒、美国粒粒橙,却唯独钟爱故里的木樨茶。古朴的茶盅盛满清甜的木樨,轻巧的银匙一拨,浮沉着艳丽如丹的花瓣,散发出沁人心腑的芬芳,喝上一口准叫人口齿氤氲留香。
木樨,亦称桂花,在我的故乡浦城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现存明嘉靖年间《建宁府志》、清光绪时期《续修浦城县志》都有记载,其花有白、黄、红诸色。开白花的如碎银簇簇,叫银桂;开黄花的似金稻穗穗,称金桂;开红花的象丹霞朵朵,唤丹桂。丹桂,可供食用。据《本草纲目》记载“桂取皮贴牙痛可断根”。《便民图纂》中说“收桂叶泡汤服温腹去暑”。桂花性温味辛,散寒破结,祛痰生津,清齿爽口,自古以来就寓以吉利美好之意。历代骚人词客对桂多有歌咏。两千多年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中,就用“结桂枝兮延伫,援北斗兮酌桂浆”来抒发依恋欣愉之情。唐代温庭筠留下“犹喜故人新折桂”的诗句,以“折桂”喻为中举登科。在国外古希腊神话中,桂作为珍品献给科学和艺术之神阿帕隆,桂枝扎成的头圈也常作为最高荣誉,奖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称之谓“桂冠”。难怪我故里的人们世代相传,把木樨茶作为清清吉吉的象征——送别和重逢,都会为您捧出一盅木樨茶。
每临中秋时节,明月悬挂中天,一树树丹金闪烁的桂花,便溶入轻纱似的月色里,夜风微拂,香飘扑鼻,使人欣欣然不想入眠,也不知是人醉在月下花香里,还是梦醒在花香月色中。在这“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美好月夜,最撩游子心弦的是浦城腔的童谣:“月光光,照四方,四方圆,卖铜钱,铜钱耀,卖乌豆,乌豆乌,卖香菇……”痴望着圆月,很易引发出故里的旧梦:收桂花的时节,孩童们唱着、闹着,在桂花树下铺开几张晒谷席,看着大人们用长竹竿往树枝叶腋间轻轻扫动,艳红的桂花便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如同一阵金亮亮的红雨,洒落在席上,也飘落到大伙的头上、肩上、脚背上,浑身沐浴在桂花的芳香里,把席上的落花扫拢来携回家,用雪白的鹅毛羽把一朵朵花蒂枝屑剔净,放在滚沸的开水里捞起,再拌上白糖浸渍封藏,待到贵客来时用开水冲泡,便成了色鲜味香的木樨茶。
如今,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浦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就设在木樨苑,糖渍桂花也由现代化机械加工出品,系列产品注册为木樨牌商标。桂花,已被定名为浦城县县花。
岁岁年年,有多少游子从四面八方回来,拾起儿时的记忆,寻觅故里的足迹。
走过五里塘,走过七星桥,走过九石渡,不管走到哪门亲戚家,见面总是捧来一盅木樨茶,又一盅木樨茶。
灼灼木樨,点点乡情,喝得心底甜甜,喝得心儿醉醉。
醉在故乡的怀抱里,仿佛又听到母亲哼过的摇篮曲。生息在这片土地,谁不想回报给这片故里更浓烈的情和爱……。
油果山记 叶志坚
油果山离我故乡仙阳镇有一里之遥,立在村口眺望,油果山有如一尊端坐的笑弥勒,坦然而温和,满山蓊盛盛的树木,荫荫络络,润润滋滋。
在我绵长的记忆里,油果山树木出奇的大,盘根曲干遮天蔽地;最多的树木是松、白枫、苦槠树,株株都有圆桌大小,幼年的我,便常翘着屁股去捡苦槠。
油果山并不高,至多海拔五、六百公尺。沿着石磴山道攀上,情趣便跟着涌流出来。那树荫,那鸟声,那汪汪吠叫着追逐山麂的猎犬;都使人神往。待攀上山巅,境界又豁然开朗:远山近水,村舍田畴,都宛如精妙画图,展现在人的眼底!那依稀残留的古驿道;小山包般隆起的二千多年前的汉阳城遗址;隔溪相望的百向山黄巢大寨;以及北宋文学家杨亿的墓地,南宋大理学家真德秀先生故居……。无不生发人的情思,无不掀动人的内心波澜!
油果山巅上凹弯之处有座残庙。庙甚古。虽然残败得只留下一座大殿,但还能看到它昔日的气势和规模。庙中,尚存着传说中周霞仙人用雨伞从杭州背来的人高褐黑碑石,以及庙旁四口青狮白玉泉。最可观的得数下殿坪院里的一株木樨,年逾数百岁,却依然躯杆挺拔,枝叶参天,每年初冬,都要开出满满一树木樨花,如霞如锦,灿烂夺目。有年中秋,正逢木樨花盛开,临时住在这庙里的一位草医,邀我在木樨花树下喝酒.不知是酒烈还是花香醉人,抑或是人的情浓,我竟喝得酊酩大醉,被人抬下山来。四野岑寂,身无所羁,不醉而何?
我是极其依恋油果山的。而今已近不惑之年,我还会时时想起当年中秋节在油果山上的那一醉。每当我有机会从煤气、漩涡、喧嚣的闹市中,或者从卑怯的笑颜里脱身来到油果山,我便宛如从窒闷的地洞里钻出,感到身心无比的愉悦。
今年春节回故乡,我又攀爬了一趟油果山。伫立山巅,极目远眺苍莽山峦,耳听四围啁啾鸟音,潺潺山泉,一时间我竟又痴醉了半晌。我想,油果山寺庙附近弃着许多梨树、茶树,要是将它们管理起来,粗菜淡饭,大约也养活一家人的。且如今旅游风日盛,听说到油果山旅游的人也不少,要是这样,在山上开个小茶铺,卖碗山茶给游客解渴,想来也是必要的了。不知有关部门是否已考虑开山铺的人选,要是可能,我倒愿意试试。事情虽小,却也是实实在在与人有益的!
题记
七十年代初期,举家四口旅居于闽北浦城县的一个小山村。村名下杉坊。连同我家,这个自然村当时只住四户人家。就当时的乡村行政体制而言,它隶属于九牧公社的杉坊大队。而此大队又辖九个生产队,共有二十个自然村。
最远的一个生产队,离下杉坊村约十华里,它在著名的渔梁岭上。那里,至今还能见到古驿路和寨门;从蔡襄等有关的诗文中可知渔梁驿至少在宋代已是一座繁华的山镇。全大队都在海拔八百至九百米的深山重岭之间,有三条山溪流经境内,其中有二条山溪便在我当时的居屋的门前汇合,出山口流入江西。溪流上有木桥,溪畔有水磨坊,林木蓊郁,鲜花遍野,鸟声时或传来。大约在1984年间,曾作一组散文,题曰《杉坊花木志》(收入拙著《给爱花的人》,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作《杉坊花鸟志》,除记述我在杉坊的所见的花木、禽鸟外,也将记述我对于那里的鱼、虫以及小山兽等的印象和感受。或可作为他日收地方志(譬如《浦城县志》)者的参考。
果子狸·夜雁
记得是1971年11月中旬来到杉坊的。先宿浦城城关一夜。竟夜大雨滂沱。次晨雨止,驱车至九牧公社报到,只见办公室内,中央置一火盆,盆内炭火融融,几位干部围在火盆边学习文件。他们见我一家人来,都让坐,且说山岭上已经下雪。
我在杉坊住下后,记得从秋暮到冬天,下过几场大小雪。若在晴日,则往往下霜或结冰。秋收以后,村里的梯田,除了一部分种上荞麦和紫云英的以外,皆裸露着,上面结着薄冰。至于霜,每在结冰之前的晴朗的深夜里下降。一天下午,我作为当时的所谓“下放干部”,参加大队党支部所召开的各生产队队长会议,内容主要是落实次年的春耕生产的种子、肥料等的分配问题。我不记得是什么缘故,直到将近半夜才结束(大家在大队部吃晚饭)。会后,我与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自然村的老王同行,一起回家。老王四十开外,满腮胡髭,山间天冷,但见他只穿一件到处补钉的旧棉衣,腰间束一条腰带,那旱烟管斜插在腰带里,却又不时取出,吸它几锅。且说这天夜间,我们从大队部出来,向下杉坊村里走去,一路上只见田埂上、篱笆上、村屋上、枯叶尽脱的乌桕的树枝上以及那些稻草垛上,一一凝上白霜。霜夜的月色格外清明。老王在全大队是爱说笑话和编造趣闻而出名的,记得那夜在月光中冒着彻骨的寒气,在村路上边走边听他讲些趣闻,忽然,他停下话,按着我的肩膀,要我和他一起蹲下来,说:
“瞧!——”
我蹲下来,向路边不远处的一座稻草垛望去,只见垛堆间有一只小山兽喷着鼻息,两只绿宝石一般的眼瞳里发出亮光;它似乎在警惕什么,似乎在思考怎么逃脱,似乎在估量目前有什么危险……
只见老王蹲在我的后面,从腰间抽出旱烟管,在地上敲着,好像小孩子那样,笑嘻嘻地:
“别怕,别怕,你尽管躲着——”
只见那小山兽却从稻草垛里闯出来,箭一般地从路边跳上附近的田埂路,一路踏着浓霜,往一片树林里躲进去。在月光下,我看见这只小山兽好似一只山猫,但体长,眼边有白色条纹。老王扶着我站起来,笑笑说:
“别管它了——等下它还会回来,躲进稻草垛里——”
他告诉我,这小山兽当地人叫它笑面狸(我查了辞典,得知学名为果子狸)。霜天,山上更冷,这小山兽便跑到村里,躲在稻草垛里取暖。据老王说,笑面狸跑到稻草垛里,有时也为了寻觅未打干净的稻穗上剩下的谷子。但它主要是吃山上野生的山楂呵、杨梅呵、野李呵。老王还对我说:
“这小家伙还会吃小鸟呢,哈!哈!”
他说,有一次在林中找蘑菇,不意树上的鸟窝里掉下一只雏鸟,没想一只笑面狸从林间跳出来,把雏鸟啣在口里,就往树林深处跑去……
记得又有一次,也是下霜的深夜,开会后,老王陪我从大队部回到我家(他总是送我到家,然后自己回去)。他在我家门口的石阶上站住,望着澄蓝的夜空,忽然说:
“你看——天上有雁阵……”
我抬头一望,真的看到在北斗星座的斗柄下,有排成人字形的雁阵自北往南飞行,我好似还听得有“咯咯”的雁鸣声,自远天传来……
老王说:
“它们从苏武牧羊的地方飞来,已飞过开封府、苏州府,正向延平府飞去,最后飞向兴化府、泉州府的海滩上去过冬……它们飞过的路远啦,嘻嘻哈!”
不知怎的,那夜久久不能入眠。心里一直在想,儿时也曾在家乡莆田(即老王所说的兴化府所在)的秋空中,看到雁阵,但感那样的岁月离我已很遥远,一如秋雁的旅途!
小麂·刺猬
那天夜里,村里下了一场可能是入冬以来最大的雪。山中有一段冬闲的日子,天又冷,这样,村民们往往在天暗后不久便闭户就睡。这场雪大约就在这时候开始纷纷飘落,可能直到夜深才止。就我自己而言,可能是所见最大的一次雪。记得当时我所居住的下杉坊村,只见四面的山峦都盖上白雪;村屋前不远处的木桥盖上白雪,溪中的岩石盖上白雪,溪边的水磨坊和一座土地庙,以及田埂路、还有晒谷场都铺满了雪;我和邻居的屋顶上更是盖着厚厚的雪,而且,早晨起来时,屋前的石阶都给雪封住了。这样的雪天,山上的雪必定下得更大,有一些小山兽便跑到村里来,寻找取暖的处所。
有一只小山麂就从山上的密林里跑下来,躲在我当时的邻居阿方伯家灶间的干草堆后面。根据一点迹象,我估计这只小山麂对于山中大雪之欲来、将降,有一种本能的预感,而且会本能地去寻找可以躲藏之所,记得当时我竟会作这样的“判断”,以为这只小山麂是在大雪下降之前,便跑到山下村里来;而且又是在阿方伯一家闭户就睡之前,便悄悄地走入灶间里的,它在干草堆后面安安稳稳地躲藏(取暖和睡觉?)了一个整夜。
记得那天得知阿方伯家里跑来一只小山麂,我立时走来看望这只小山兽。只见阿方嫂坐在灶下,边用刈稻刀切着干草,边喂着那只躺在她身旁的小山麂;只见它卟哧卟哧地喷着鼻息,好像感到十分可口地嚼着干草。我似乎还是初次见到一只小野兽和人能够处得这么亲近;并且,当我走近它时,它似乎也不感到陌生和畏惧……
我不觉随口说了一句:
“何不如把这只小山麂养下来……”
听了我的话,站在一边尽是吸着旱烟管的阿方伯,笑笑道:
“还是要把它放回山上去的!——”
我仔细地观察一下这只小山兽,感到它有点像鹿,但体形比平日在动物园里所见的梅花鹿小得多;其毛,背呈棕褐色,腹呈白色,油润而光滑。我感到它很可爱。却见阿方伯抚着它的头,又笑笑说:
“你看,它头上无角,是只雌的——放它归山,可以传子传孙,哈哈哈!”
在整个杉坊大队,这位年约五十余岁的农民阿方伯,都受到尊敬。有人说他能知天文,说他看星、看云、看天色,能知若干天内的气象。他还熟悉当地的水利以及传闻轶事和民俗。有空时我喜欢和他闲谈,感到他的随意谈吐间,常常出现一种山地农民的幽默感,又含有某种朴素的民间深意。那天,他还告诉我,按照村里自古以来传下的习俗,凡山上有小兽躲到屋内来,不论是为逃避猛兽的追逐而来,还是为逃避某些祸害(譬如山中风雪等)而来,均不得杀害,且要挂红送回山上……
这只小山麂被养在阿方伯家两天两夜。阿方嫂每天给它喂谷物、干草。第三天,雪开始消融了,早上便出了太阳。阿方伯找到一方红布,系在小山麂的耳朵上,自己怀抱着,准备放在村里的土地庙前,然后让它跑过山上的密林中去。下杉坊村的一些村民,包括我这位“下放干部”,都陪同他一起给小山麂“送行”。我们走过木桥,走过长长的一段溪边的小径,正走近水磨坊时,阿方伯忽然停下脚步,他似乎听见水磨坊内仿佛有什么动静……——原来是一只刺猬躲在水磨坊的小房里面;它大概听见人声(以及人的气息?),下定决心从里面冲出来;只见它喷着鼻息,隆起全身的针刺,像突围似地冲出来,几箭步便冲在土地庙前,然后沿着被融化的雪水浸蚀的小泥路向密林中逃去……
对那逃荒似的刺猬的背影,阿方伯笑笑说:
“别慌,别慌——只要你不偷走地里的番薯,不会抓你的……”
有人在水磨坊的小房里看一下,只见地上有一大堆灰烬,是舂米的村民烧木炭取暖时留下的灰烬。这只刺猬大约便躺在这灰烬上度过寒冷的积雪的夜晚?
再说大家跟着阿方伯把小山麂送到土地庙前后,便放它自己往山上的密林中跑去。却见这只小山麂真像有心人一样,跑了几步,便站住回头看看大家——最后才跑进林中,不见了。记得在杉坊时,我有时感到某些小山兽能察人意,能与人亲近;有些小山兽,对人则永远保持距离,永远对人保持警惕。
杜鹃花·虾·竹鸡
多次想到西源垅去走一趟,好好地看一看,但总被别的事耽搁了。西源垅是杉坊大队的一个狭长的山垅(沟),有一条山溪从这里的山间流出来。想到西源垅看看,有若干原因,譬如很想实地观察那里的自然环境以及到独户住在那里的老杨家里去坐一坐,等等。老杨本人曾多次约我到他家里看看,这中间更仿佛出现某种需要履约的情分,使我难以忘怀。记得是清明节后的某一天上午,我一人沿着溪岸陡坡上的小径,随意漫行,且看,且在笔记上写下一点记录,有时便坐下休息,准备在午饭前来到老杨家里。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开放的杜鹃花,自是在杉坊大队这一带地域内。从我当时居住的下杉坊村,南至渔梁岭,北至九牧公社,遍山遍坡,一座山峦联着一座山峦,视线所及,我觉得满目都是血红色的杜鹃。有一次我到九牧公社去开会,途中曾见到若干山岩上只要有一点泥土,便会长出小棵的杜鹃,并开放血红的花朵。据我现在的回忆,整个花期长达二十余天。不过,据当地群众所称,杜鹃花开放得最旺的还是西源垅一带。那天,我一进入西源垅,便见从山口开始,沿溪的山坡上全是杜鹃花。其间,我很快发现,而且全是一种灌木,有的甚至高达五、六丈,花形看来也较为硕大。最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在满山灿烂的血红的花朵中间,见到有的杜鹃开放的却是雪白或桃色的花朵;更见到在杜鹃树下,金银花也在开放花朵。
记得那天我是沿着溪流北岸的斜坡深入西源垅里。在垅内行了大约三华里,岸边出现一片开阔地。不知怎的这开阔地长着矮矮的、褐色的不知名的小草,无树木。远远地,我便望见那天阔的草地上有一群斑鸠在觅食草籽,它们咕咕地叫,至少有二百余只。这又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一群斑鸠。和我小时在家乡莆田所见的斑鸠相比,它们体形较小,颈部的羽毛呈灰蓝色,很有光泽。当我走近时,它们也不高飞远走,只是各自转身向四面稍为分散飞开;待我稍为走远,——我回头一看,它们又都飞回草地上觅食,并且咕咕地叫。我心里想,这大群的山斑鸠,好似知道我是不会损害它们的;但当时我又想,这是一群警惕性不高的山禽?记得离这片草地大约又二华里,有一道用三根树干拼成的木桥,从岸上搭到溪中的一堆大岩石上。过此桥,便走向南岸。桥下溪水汩汩,激着错列的溪石,溅起水花。不知怎的,当时忽生一奇怪念头,即想蹲在桥上观察溪中的“动态”。有趣的是,居然见到一只溪虾。它全身呈一种透明的灰绿色,长约八厘米,头上有很长的触须;我见它一动不动地停在水中一块平滑的溪石上,有时稍稍地动一动触须。我至今还想不出来,这只虾何以一直静静地停在那里?
溪的南岸有一些梯田,村民称之曰“山垅田”。这山垅田原来只宜于种单季稻,但当时有关方面,却强制推行双季稻的种植,虽然有不同意见,但被用“保守思想”的帽子压下来。这样,自古以来不种双季稻的山垅田,这时节也种下秧苗,并且正在发青。一路上,我想着老杨当时曾因对在山垅里种双季稻,在思想上不通受过批评。但村民们却因此更看重他……我边想边走,沿着山路向老杨家里走去.不想,我过桥后才走了一段路,老杨和他的一只纯乌毛的猎犬,便从前方向迎我而来了。像村里的一些中年农民,老杨也满脸胡髭,吸旱烟管。我初到杉坊时,便听人说过,老杨一对公婆独户住在西源垅,主要是为便于打野猪,好保护山垅里大片梯田的收获。又听说,老杨枪法虽好,但只打野猪,山上一禽一兽,全不损害。甚至有人说,山垅里的有些野禽野兽还和老杨交成朋友呢。记得那天到他家里,只见屋后山上种了一片杉木林,又种一片竹林,都管理得很好。家里还养了三、四只鹅,一见我来,便咯咯地冲上来,好似要咬我的腿。老杨说:
“山上有蛇,养了鹅,蛇不敢来了——”
据老杨说,鹅吃的全是山上的草,其中有的草能治蛇毒,且为蛇所畏惧,鹅粪中含有这种草的渣,蛇一见到(嗅到?),便不敢来……
那天,老杨留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喝清明前刚焙的新茶。这午饭真别饶趣味,除干饭外,汤都是用临时在门前的水沟里抓来的泥鳅、黄鳝等做的。午饭间,老杨忽然站起来,向灶堂外面的竹林里,呼鸡一般地唤着,却见从竹林中走出一群竹鸡;它们有鹧鸪那么大,全身是褐色的羽毛;它们咯咯地叫着,争吃着老杨抛去的饭团……
后来我知道,老杨在早上或午间用谷物或午饭喂养竹林中的竹鸡。说也有趣,时日一久,这些山禽一听老杨的呼唤声,便从林中跑出来了,好像家禽一样。我有时想,这位老杨不仅是农民,更是一位对于山禽山兽怀有某种特殊感情的猎人。
飞雪的春节 何为
又是飞雪迎春的时节了。
那一年,我的家在山林深处。村屋依傍着山岗岩壁。大门外,奇幻多姿的武夷山脉鹫峰支脉举目可见。院子前有一棵百年大樟树,盘根错节的老树下,环抱着一口古井。这里是山区农民到浮桥小镇去的一条必经之路。往来的过路人往往在浓荫覆地的水井旁歇脚休憩。
我的家属于这个小山村的第二十七户。前边围着高高的棕色土墙,墙内重重院落把各家连在一起,俨然自成一个山寨。据老人说,多年以前,一个来自外省的卢姓拓荒者,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脚下披荆斩棘开辟一块耕地。过了几代人,逐渐形成一个自己的村落。又因为地处溪滩的拐弯处,就相沿称之为卢家湾。
我们刚搬到时,颇惊异这陌生山乡的熟悉地名。卢家湾这个地名,有如从记忆深处迸出的一声回音,骤然唤起我在上海漫长岁月里的无尽思念。那个大城市也有卢家湾。那时候全国城乡都蒙受苦难,我有一种奇异的乡愁。
经过大风暴初期的动乱日子以后,我终于被放逐到这样一个僻远的山乡,来参加劳动,而且终于在这里安了家,实在是一种当年难以祈求的“幸福”。回想在那些灾难的岁月里,不知多少人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同我住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下放干部就是我的妻子,还有在身边的女儿。我们一家三口享有一个有灶头的厨房。旁边一间土屋当作寝室。正屋有一耳房是一间朝南小屋,厚实的土墙上半截,横列着一排整齐的木档。我们取一块卷铺盖的塑料薄膜把宽阔的窗户严严遮住,既可聊蔽风雨,又可照入阳光,成为极富有装饰意味的窗棂。这间在山村里少有的明亮土屋,我们用来兼作卧室和书房,也是接待左右邻居的所在。
那时,我们都喜欢这个远离尘嚣的僻静的农村之家。我的妻子下乡时,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农村医疗手册,自己又置备了一些常用药物,以防不时之需。一次,沉默寡言的老生产队长站在门槛边半天不说话,一看才知道他出工不慎踩着竹尖,脚底全是血污,当即给他作了消毒处理,并用纱布包扎了一下。又一次,房东大娘的孙女儿芳婷患感冒发烧,量过体温,配了一些扑热息痛及长效磺胺之类交给他们。以后不断有人上门来索取一点药,或者要求涂点消炎药膏,我们这间小屋竟又成为简易的医疗室。
那些整年累月在山地默默劳作的农民们,平时为了买一斤粗盐的钱都得到处张罗,轻易是不愿到七里地的小镇卫生院看病的。开头几天,他们多半很拘束地侧立门旁,难得跨进我们的小屋。但是数月后,除了生产队干部带到这屋内研究队里的工作以外,就有一些大婶大嫂带着孩子找上门来,高高兴兴地坐在屋里闲话家常了。在我们自制的小油灯火光摇曳下,经常是一壁厢笑语人声,一屋子人影晃动。
不久就临近春节。过了阴历十二月半,生产队里的年终分配大抵已接近尾声。人们胼手胝足劳动了整整一年,现在家家户户开始蒸年糕,酿米酒,炒花生,做芝麻糖等等。那怕仅仅是一种节日的点缀,一种传统年景的象征。这个生产队历来种籽瓜,以瓜子颗粒大而饱满闻名远近。在柴火哔剥的大灶头上,热铁锅里炒瓜子的声音,是多么富有魅力,谁听了都会感受到过年的欢乐气氛。
山区的冬天严寒逼人。我们的小土屋里,烧着一盆炽热的炭火。火光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作玻璃的木槅窗。窗外是一角灰蒙蒙的欲雪景色。已经是岁暮年边,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那两个在少年时代就过早地离开学校,到另一处山区去插队劳动的男孩,不是来信说回家欢度春节吗?做母亲的不知多少次站在大樟树下举首翘盼。她心神不宁地刚刚回到灶头旁,忽然小女儿雀跃地大声欢呼起来,向外飞奔。在微雪的幽明中,两个肩挑重担的少年推开了自己的家门,把他们这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收获都挑回家来,回到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家里。
这在小山村也是一件新闻。许多相熟的农村妇女纷纷进门来探视,看看下放干部全家团聚的情景。心地忠厚的房东大娘,从我们住在她家里的第一天起,便处处关心我们。她大约六十多岁,终日忙个不停,善于在不同节日里做各种美味的农村传统食品,以她的巧手和为人热诚,受到全村的尊敬。她正在热气腾腾的蒸笼旁,忙着帮我们家做红糖年糕,这时一转身从她的住屋里捧出一大包炒花生,非要塞到我的两个儿子手里不可。过了一会,老队长特意拿来一瓶家酿的桂花米酒,默然无语就悄悄离去了。随着邻居们亲切的问询,不断送来油麻糕、寸金糖和糯米团,各种各样家制的糖食和糕点。啊,善良的、纯朴的、可亲的山区农民们,你们送来岂止是最好的节日食物,还有一片使人为之感动的真切情意。
大年夜落了一场瑞雪。繁密的雪花闪闪烁烁地漫天飞舞,整个山村笼罩在沉静的飞雪之中。在这仿佛与世隔绝的山乡,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年饭,随后一家人围住满盆炭火。火盆上的水壶冒着热气的氤氲,伴随着沸水欢乐的嘶嘶作响。红烛初燃,笑语盈室。真的,我们记不起那一年的除夕比今夜更温暖了。
然而,在这飘雪的岁末之夜,在远离我们小屋以外的全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有多少团聚的家庭,又有多少离散的家庭?多少人有家归不得?多少人无家可归?我们凝视着明亮的炭火,怀念失去音讯的亲友故旧,默默祝愿他们都能欢度这新春佳节,愿祖国大地上的人民在未来的每一个春节都吉祥如意。
大年初一的清早是在爆竹的脆响声中醒来的。睁眼一看,呀,整个小土屋都是银亮的雪光,横窗上嵌着白色花纹似的雪花,屋檐凝结着白珊瑚般的冰串。我们迫不及待地推开小院的大门,门外是一个广漠的白雪世界,白得宁静,白得肃穆。真想去拥抱这洁白的大地。一股清冷的新鲜空气迎面扑来,不知怎么想起学生时代喜欢的惠特漫一句诗:
“啊,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
这个年初一的雪朝,我们在满头皆白的大樟树下走过。遥望溪流对岸,白皑皑的群山屏立,象一幅银灰色调的庄严版画。踏着雪,走到溪边渡口去的曲径小道,厚厚的积雪印上我们一家人蜿蜒的足迹。渡口那棵满是冰雪的大树上花开满枝,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一树迎着严寒来报春的是梅花!
山林深处的卢家湾,别来无恙否?你在我们最感到孤零的时候给我们温暖,你在我们最寂寞的春节中带给我们最难以忘怀的节日愉快。你是我的第三个故乡,还是第四个故乡?也许有一天,我将在那个大城市里的卢家湾想起你。我一定会想念你的,在每一个飞雪迎春的日子里。
故乡的梦 季仲
我的摇篮
从崇山峻岭中的汩汩淙淙地走到平原上来的南浦溪,是我幼年的摇篮。
那潺潺的溪水,明净如水晶,莹洁如碧玉,温柔得象母亲贮满了爱的眼睛。
夹岸的桃花、垂柳以及生机勃勃的芦苇、马鞭草和箭竹林,为我的摇篮装饰着织锦一般的花边。
蓝天、白云、朝霞、暮霭以及雨后初霁横贯长空的七彩长虹,常常装满了我的摇篮,变幻出一个无限辽阔而神奇的童话世界,引起我这个小傻瓜多少天真、高远的遐想呀!
我曾和我的穿开裆裤的小伙伴们,在溪流里学会“狗爬式”;
我曾跟随老渔翁驾一叶竹筏,停在江心看鹭鸶叼起欢蹦乱跳的大鱼;
我曾拽着水牛的尾巴,闯过急流飞湍的漩涡。
溪滩上,夏夜蟋蟀们的鸣叫,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优美的奏鸣曲;
溪埠头,朝霞辉映下的浣衣女,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动人的水彩画;
而那风雨如晦的沉沉黑夜,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农妇跳溪自尽的悲剧,则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启蒙课。
呵,亲爱的南浦溪,你琼浆玉液般的乳汁哺育着我。整个孩童时代,我在你的怀抱里作过多少次温馨的梦!
呵,亲爱的南浦溪,你母亲一般的爱是深沉的、博大的,你养育了你的儿子,却不会娇宠你的儿子,让他蜗居于一个小小的天地。儿子长大了,你掀起你透明的风,扬起我年轻的帆,沿着蜿蜒曲折的航道,穿山越谷,击水南下,驶入闽江,停泊在一个书写着我们民族的光荣与耻辱的海口。
于是,我见到了碧波万顷的茫茫大海,见到一个辽阔恢弘的大千世界。
然而,南浦溪呵,我童年的摇篮!至今我仍常在梦中,听见你的溪滩上的蟋蟀的吟唱,看见你的清流上那流萤一般的渔火一闪一闪。
山中的海
我是山的儿子。
我外婆家在很高很高的高山上。那里满山遍野都是翠生生的毛竹。
小时候,我没见过海。但在我的想象中,这无边无际的毛竹林,不就是绿色的海——山中的海吗?风和日丽的日子,凤羽状的竹枝竹梢,纹丝不动,竹林里悄无声息,静得象深不可测的海底。
风狂雨骤的日子,每根毛竹都被刮得前伏后仰,发出惊涛骇浪的唿啸,显示出大海的粗犷而雄伟的气魄!
我记得,我曾和我的小伙伴们在竹林里拖过毛竹,挖过冬笋。我还记得,用笋壳的小尖儿做成的小笛子,能吹出一种迷人的、温馨的、带着乡土气息的曲调。
我记得,我外婆村里的舅舅姨姨们都是能工巧匠。他们一拿起平平常常的篾刀,就都变成神通广大的魔术师。纤细如发、柔软似绸的篾丝,从他们手下流出来,流出来,在地上浮起一片带着清香的云彩。他们编织的花篮,象花一样,散发着芬芳的气息;他们制作的鸟笼,即使没有画眉鸟儿,也会唱出许多醉人的歌。
呵,至今我的书案上还放着故乡青竹做的毛笔筒。每当看到它,我就深深地怀念那一片绿色的海,故乡的海,山中的海。
木偶大师
他是全才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大师。
在村寨的祠堂里,或小小的晒谷坪上,他和他的助手仅用四张八仙桌,或几块长木板,搭起一个小舞台,拉起一块绣着“天官赐福”的帷幕,就能撑起一个具有非凡艺术魅力的大剧院。
于是,他就能给淳朴善良的山民们带来历史和文化,带来神话和童话,带来诗和音乐,带来生活的欢欣、慰藉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能够扮演生、旦、净、末、丑所有行当。他还兼任着编剧和导演。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流动剧团。
在我的记忆里,他唱花木兰,赛过常香玉;他唱黑包公,赛过李少春;他掌中的三花脸儿,滑稽、诙谐、风趣、刁钻,集我生活中见到的可爱与可憎的人物种种妙处于一身,憨态可掬,美不可言,比起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也毫不逊色。
他那灵巧的五指牵动木偶们作出捋须,甩袖,骑马,挥鞭,舞剑,厮杀……等等动作,情态毕肖,栩栩如生,真不亚于一个造诣精湛的优秀演员。
我还没到上学年龄,就从他的表演中认识了孙悟空和猪八戒,梁山伯和祝英台;就记下了《三顾茅庐》和《林冲夜奔》等许多历史故事。
他那魔术师的手指和金属一般经久不衰的好嗓门,给我多少欢乐,多少智慧,把我带到一个多么奇妙的幻想世界!
啊,即使我在首都一流的艺术剧院欣赏过一流的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我还要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故乡的木偶戏,不会忘记那位全才的杰出的却名不见经传的表演艺术大师!
山城水清清 沈世豪
位于闽北山区的浦城,素有“小苏州”的美称。最令人留恋的,是城里的水。
浦城是山城,老城是沿着仙楼山而建的。小巷深深,夹巷一律是青灰色砖墙,又称风火墙。倚墙的庭院,很有气派,几进几出,最大的竟住了九十九户人家。清粼粼的南浦溪绕城滚滚流去,人们毫不足惜。因为,城里有井。最驰名的一口,叫清水井。以前,这里人喝水是很讲究的,只喝清水井里的水。这口井在老城正中,又称学前,那水清冽冽的。城里人待客、迎客的不是茶,而是泡一杯糖桂花。杯子是无色玻璃的,滚烫的水刷地冲下去,桂花瞬间全开了,鲜灵灵的和活着的一模一样。主人笑盈盈地递过一支花瓣状的长柄小银匙,轻轻一搅,红艳艳的桂花开得生意盎然,扑鼻的清香,丝丝缕缕,浓浓淡淡,悠忽沁人心胸,又悄然弥漫开去。品一口,余味无穷,仿佛消融在一派氤氲的香韵里。这都是因为清水井的水好。不信,你试用南浦溪水泡泡看,不仅桂花不鲜,而且还有一股水腥味哩!
城里新建的高楼,以及颇有气派的机关大院,是不乏自来水的。全县虽设有自来水公司,许多单位都备有抽水设备,但人们还是喜欢喝清水井的水。每当早晨,或是傍晚,到清水井挑水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窄窄的老街,铺着麻石,两旁是斑斑驳驳的木骑楼。挑水的人多了,水溢出来,濡湿了街道,乍看去,潮润润的,既觉得故里的温馨和亲切,又觉得古城淡淡的悠远和闲适。远走异国他乡的山城人,恋情绵绵不绝,这街道,仿佛铺在游子们心灵的深处。清水井也奇,无论多少人挑,从来没有干涸过,终年水清,纤尘不染,更不消说有一粒泥沙了。因而,也不必“洗井”。人世沧桑,这清水井,总是那么坦坦荡荡、盈盈的,仿佛藏着一个迷人的秘密。
闽北的山城多,数浦城文气重。历代人材辈出,状元且不去数它,仅在宋朝,就出了八个宰相。城内的孔庙,巍峨壮丽,金碧辉煌,不仅在闽中首屈一指,而且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数米高的孔子塑像,温文尔雅,栩栩如生,塑像的泥土,取自数千里之外的孔子故梓曲阜。不幸的是,“文革”中的一炬,声名显赫的孔庙竟夷为平地。人常说,地灵人杰,山城的老年人爱谈古,免不了论论风水阴阳。往往又牵扯到清水井,都说是这水养人。我不信,曾和一位远房亲戚论过。
“你不信么?”他用眼睛乜斜着我。愤懑、鄙夷,甚至有点动怒了。仿佛我是一个背叛列祖列宗的逆子。
“你细细地看看,这清水井养出来的姑娘都特别漂亮。”他忽然又找到了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我们一齐笑了,这可是真的。浦城的姑娘长得美,肤色好,水灵灵的,洁如凝脂。高高的身量,婷婷娉娉,素雅高洁,象绿竹青青,象涧水潺潺,别有一番迷人的韵致。浦城话也好听,柔媚而不乏刚健,细软而又不嗲声嗲气,既有吴越方言的甜润,又含闽粤客家的质朴。尤其是女声,更是动人三分。浦城姑娘爽朗,如五月的武夷山,眉清目秀,而不象深居闺阁的淑女,羞羞涩涩,她们爱美,并不着意在衣饰上精心打扮,而是善于用自己的巧手,描绘明明净净的山水画。人爱清水井,那清粼粼的水,莫非亦钟情于山城的灵秀么!
少年时代,常去清水井挑水。井台高,井深不见底,只看到井壁内厚厚的青苔。汲水是极有功夫的,因为看不见井里的水,只凭手中吊桶上绳子触觉。汲水的吊桶放下去,放下去,蓦地,从水井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呼地一声响,手中的绳子也仿佛失去了重量,只须轻轻一抖吊绳,约莫三、四秒钟,水便汲满了,麻利地将吊绳在手腕上缠上两圈,猛地吊上来,两手交叉地提呀提呀,扑面一股凉意,转眼就将水提将上来。颤悠悠地挑着一担玉露似的水,从熙熙攘攘的闹市穿行而过,自有几分快意。
也有孤寡人家,缺乏体力,便雇人去挑。若论担数,一担只须二三分钱,也有按月数的,价钱更是贱得很。我认识一个专以挑水为业的哑巴,人们不知他姓什么;只叫他“哑子”。他是汲水里手,只见他口中含着香烟,手中吊绳只一抖,腰也不弯,不出三秒钟,满满的一桶水便轻而易举地提将上来。偶而,逢到体弱的老人和小孩前来挑水,隔着几尺远,他头也不抬,把将上来的水,整桶倒过去,刷地掠起一匹弧形的银练,待你清醒过来的时候,一桶水滴水不溅地落在你的水桶里。人们往往带着嗔笑感激地说:
“这哑子——”
他是听不见的,仿佛不当一回事,手中的吊绳一抖,一桶水又汲上来了。我很赞叹他那一手绝技,更由衷地敬佩他那象水一样纯净无瑕的心。我曾到他家去玩。他最爱吃豆腐,平时,极少吃饭,往往是以豆腐当饭的。清水井水好,做出来的豆腐也特别鲜嫩,细心的哑巴,可能是真正品出味儿来了。
转眼一二十年,哑巴不知是否还在人世?远在异地,闲暇时节,也牵起淡淡的乡愁。浦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了,但清水井还在。山城水清清,汩汩,森森,点点滴滴在心头,更分外撩人思绪哩!
故里,捧出一盅木樨茶 祝文善
不管你去到多远的地方,不管你离别多久的时光,故里,总像一块巨大的无形的磁场,紧紧吸住游子拳拳之心。
谁也不曾想到,回故乡的路竟然走过多少岁月!海峡两岸的藩篱,隔不断血浓于水的乡情,一位又一位海外游子,一批又一批去台人员,终于回到生养自己的闽北浦城。不知为什么,品尝过法国白兰地、英国威士忌、日本清酒、美国粒粒橙,却唯独钟爱故里的木樨茶。古朴的茶盅盛满清甜的木樨,轻巧的银匙一拨,浮沉着艳丽如丹的花瓣,散发出沁人心腑的芬芳,喝上一口准叫人口齿氤氲留香。
木樨,亦称桂花,在我的故乡浦城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现存明嘉靖年间《建宁府志》、清光绪时期《续修浦城县志》都有记载,其花有白、黄、红诸色。开白花的如碎银簇簇,叫银桂;开黄花的似金稻穗穗,称金桂;开红花的象丹霞朵朵,唤丹桂。丹桂,可供食用。据《本草纲目》记载“桂取皮贴牙痛可断根”。《便民图纂》中说“收桂叶泡汤服温腹去暑”。桂花性温味辛,散寒破结,祛痰生津,清齿爽口,自古以来就寓以吉利美好之意。历代骚人词客对桂多有歌咏。两千多年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中,就用“结桂枝兮延伫,援北斗兮酌桂浆”来抒发依恋欣愉之情。唐代温庭筠留下“犹喜故人新折桂”的诗句,以“折桂”喻为中举登科。在国外古希腊神话中,桂作为珍品献给科学和艺术之神阿帕隆,桂枝扎成的头圈也常作为最高荣誉,奖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称之谓“桂冠”。难怪我故里的人们世代相传,把木樨茶作为清清吉吉的象征——送别和重逢,都会为您捧出一盅木樨茶。
每临中秋时节,明月悬挂中天,一树树丹金闪烁的桂花,便溶入轻纱似的月色里,夜风微拂,香飘扑鼻,使人欣欣然不想入眠,也不知是人醉在月下花香里,还是梦醒在花香月色中。在这“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美好月夜,最撩游子心弦的是浦城腔的童谣:“月光光,照四方,四方圆,卖铜钱,铜钱耀,卖乌豆,乌豆乌,卖香菇……”痴望着圆月,很易引发出故里的旧梦:收桂花的时节,孩童们唱着、闹着,在桂花树下铺开几张晒谷席,看着大人们用长竹竿往树枝叶腋间轻轻扫动,艳红的桂花便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如同一阵金亮亮的红雨,洒落在席上,也飘落到大伙的头上、肩上、脚背上,浑身沐浴在桂花的芳香里,把席上的落花扫拢来携回家,用雪白的鹅毛羽把一朵朵花蒂枝屑剔净,放在滚沸的开水里捞起,再拌上白糖浸渍封藏,待到贵客来时用开水冲泡,便成了色鲜味香的木樨茶。
如今,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浦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就设在木樨苑,糖渍桂花也由现代化机械加工出品,系列产品注册为木樨牌商标。桂花,已被定名为浦城县县花。
岁岁年年,有多少游子从四面八方回来,拾起儿时的记忆,寻觅故里的足迹。
走过五里塘,走过七星桥,走过九石渡,不管走到哪门亲戚家,见面总是捧来一盅木樨茶,又一盅木樨茶。
灼灼木樨,点点乡情,喝得心底甜甜,喝得心儿醉醉。
醉在故乡的怀抱里,仿佛又听到母亲哼过的摇篮曲。生息在这片土地,谁不想回报给这片故里更浓烈的情和爱……。
油果山记 叶志坚
油果山离我故乡仙阳镇有一里之遥,立在村口眺望,油果山有如一尊端坐的笑弥勒,坦然而温和,满山蓊盛盛的树木,荫荫络络,润润滋滋。
在我绵长的记忆里,油果山树木出奇的大,盘根曲干遮天蔽地;最多的树木是松、白枫、苦槠树,株株都有圆桌大小,幼年的我,便常翘着屁股去捡苦槠。
油果山并不高,至多海拔五、六百公尺。沿着石磴山道攀上,情趣便跟着涌流出来。那树荫,那鸟声,那汪汪吠叫着追逐山麂的猎犬;都使人神往。待攀上山巅,境界又豁然开朗:远山近水,村舍田畴,都宛如精妙画图,展现在人的眼底!那依稀残留的古驿道;小山包般隆起的二千多年前的汉阳城遗址;隔溪相望的百向山黄巢大寨;以及北宋文学家杨亿的墓地,南宋大理学家真德秀先生故居……。无不生发人的情思,无不掀动人的内心波澜!
油果山巅上凹弯之处有座残庙。庙甚古。虽然残败得只留下一座大殿,但还能看到它昔日的气势和规模。庙中,尚存着传说中周霞仙人用雨伞从杭州背来的人高褐黑碑石,以及庙旁四口青狮白玉泉。最可观的得数下殿坪院里的一株木樨,年逾数百岁,却依然躯杆挺拔,枝叶参天,每年初冬,都要开出满满一树木樨花,如霞如锦,灿烂夺目。有年中秋,正逢木樨花盛开,临时住在这庙里的一位草医,邀我在木樨花树下喝酒.不知是酒烈还是花香醉人,抑或是人的情浓,我竟喝得酊酩大醉,被人抬下山来。四野岑寂,身无所羁,不醉而何?
我是极其依恋油果山的。而今已近不惑之年,我还会时时想起当年中秋节在油果山上的那一醉。每当我有机会从煤气、漩涡、喧嚣的闹市中,或者从卑怯的笑颜里脱身来到油果山,我便宛如从窒闷的地洞里钻出,感到身心无比的愉悦。
今年春节回故乡,我又攀爬了一趟油果山。伫立山巅,极目远眺苍莽山峦,耳听四围啁啾鸟音,潺潺山泉,一时间我竟又痴醉了半晌。我想,油果山寺庙附近弃着许多梨树、茶树,要是将它们管理起来,粗菜淡饭,大约也养活一家人的。且如今旅游风日盛,听说到油果山旅游的人也不少,要是这样,在山上开个小茶铺,卖碗山茶给游客解渴,想来也是必要的了。不知有关部门是否已考虑开山铺的人选,要是可能,我倒愿意试试。事情虽小,却也是实实在在与人有益的!
相关地名
浦城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