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因众望初当先生悯孤儿三访大嫂
| 内容出处: | 《朱熹书院与门人考》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945 |
| 颗粒名称: | 第十一回 因众望初当先生悯孤儿三访大嫂 |
| 分类号: | I247.53 |
| 页数: | 8 |
| 页码: | 82-89 |
| 摘要: | 本文记述的是游生忠著的长篇小说千秋雪第十一回因众望初当先生悯孤儿三访大嫂的情况。 |
| 关键词: | 先生 悯孤儿 访大嫂 |
内容
游酢回到家中,继续帮家里干一点农活,有时也与周围的青年朋友交往。
五月的一天,游酢去朋友家回来,进门便看见一个国字框脸庞,英气勃勃的十六七岁少年,游醇说:“俗话说来得早,还不如来得巧。”转身问那青年:“猜猜这人是谁?” 那个少年摸摸脑袋,说:“猜不到。” 游醇说:“我介绍一下吧,此人就是鄙人的堂弟,名酢,字定夫。”又向游酢介绍道:“此君姓陈,名灌,字莹中,号了翁,剑州沙县人。你们有缘吧。”陈灌连忙起身拱手道:“久仰、久仰!”,游酢听出陈灌的口音比较生硬,但是还可以辨别出语音的含义,于是回礼道:“彼此、彼此!请坐!” 两人互相问好之后,陈灌问道:“游君青春几何?”游酢谅他年龄相差无几,应道:“皇祐五年的。”陈灌听罢,拱手道:“我小四岁,当称游君为兄矣。”游醇介绍说:“定夫,你不知道,陈君可算得上是一个书香门第、缙缨世家。其远祖陈雍为唐朝御史中丞,本朝有故吏部尚书陈世卿、还有谏议大夫陈称等名宦。”游酢听了拱手道:“贵府确实了得,令人景仰之至。”陈灌心里知道自陈雍迁居固发口以来,陈家可谓人才辈出。可是,他却回答道:“祖上和家族好,不等于我好啊。要是我当乞丐,谁瞧得起?人得靠自己争气。”游酢问道:“陈君的家就在沙县?”,陈灌回答说:“不,在沙县南面两百多里的固发口,俗称‘挂口’。”游醇说:“我有一点事情要办,你们先聊吧。”通过一番交谈,游酢听出了闽北方言与闽西北方言有差别,可是不很大,仔细听还是能够辨得出话意的,如“沙县”一词听起来,听起来像“傻嫌”似的。
于是,两人互相询问了对方的家庭情况、家乡的风土人情。
过了半个多时辰,游醇回来了。三人接着又闲谈了一些读书的事情。
夜有一点深了,游酢知道家里的房间少,游醇已经有妻子和一个儿子,提出说:“大哥,陈君晚上就到我那儿睡。”游醇应道:“好吧。” 这一天夜里,游酢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归宗岩等,陈灌也介绍他家乡栟榈的风景和传说。游酢听了道:“如此神奇之地,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陈灌说:“现在就是机会,以后成了家或者到外面去做事情,就不一定有时间玩。明天叫你哥哥也一起去。”游酢回答道:“目前,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帮忙,下次再说吧。”陈灌听了,说道:“那好,我随时欢迎你去。” 第二天,陈灌便上路回家了。
一连天晴,半个月不见滴雨。白天热得狗直吐舌头,猪在栏里嗷嗷叫;晚上,屋里像炭窑似的。夜间,田野里到处青蛙“贡贡”鸣叫,此起彼伏,乡村的人们不分男女,大多都在自家的坪子上纳凉,人多的场所就听人讲故事。年轻人在家待不住,挑着松明火把出去,有的到田间叉泥鳅,也有的去抓青蛙,到了半夜回来煮了吃;有的则到山林中溪涧抓石蚌。他们大多的是抓来卖钱,到了山中顺着坑沟摸去,希望抓得越多越好,可以卖更多的钱,所以一般都要到天亮才回家,早晨去卖,下午睡觉。
转眼到了六月,游复患病瘫痪在床,书斋只好停了。游醇、游酢听说,连忙前往看望。
游复拉着游醇的手说:“质夫、定夫,你们看我这个样子,你帮忙接手把书斋办下去吧。”游醇犹豫了一下,安慰说:“叔,你先好好养病,也许到了秋天会恢复健康。”游复灰心丧气地说:“我恐怕好不了。”游酢也安慰说:“叔,你身体一向很健,一定会好起来的。” 傍晚时,游酢看见三叔在劈松明,于是问:“晚上去叉泥鳅?”三叔回答说:“是。你要是去,可得把松明火给我点旺旺的。”游酢答道:“听你的。”三叔笑着说:“好,天黑就去。” 天黑后,三叔一手拿着一把铁叉,一手挑着火篓,左肩还背着一个装泥鳅的竹篓,把一只装松明的竹篓递给游酢,说:“走!”游酢接过竹篓背在右肩上,说:“叔,我帮你拿火篓。”三叔说:“不要,等开始要叉泥鳅时,你再帮我抬火篓。”于是,三叔在前,游酢后面跟着。
夏夜很闷热,田野里昆虫在唧唧低鸣,远处传来一阵阵青蛙的鸣叫。虽然是月初,看不见月光,夜空却繁星密集,地面不见一点亮光。在田间走着,游酢问道:“为什么要晚上叉泥鳅?”三叔说:“天气热泥鳅会爬出来歇凉,在田里会留下痕迹,一条条长长的,灯火一照就现出来。照着痕迹叉去,准有的。”他又问:“刚才的田为什么不叉?”三叔应道:“你读书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肥田才有泥鳅。”松明油脂多易燃,走了一段路三叔便给火篓里添一小块松明。到了一份财主的田,三叔把火递给游酢,说:“你和我平肩走,我叫停,你就站住,等我叉完了泥鳅再前进。把鞋脱在这里,回头再穿。下田的时候要看,别把禾苗踩坏了。” 那泥鳅叉是铁的,头部只三四寸长,靠开口约一寸半两边锋利,进去越来越小。泥鳅虽然很滑,一旦被叉住,身体越挣扎就便往刀刃掐得越深。三叔是叉泥鳅的老手,眼尖手快,一下田便叉了一条,提起叉将泥鳅放进竹篓里。叉起第二条时,游酢好奇,说:“叔,我来!”他伸出手要将泥鳅抓出,结果泥鳅一溜掉到田里游走了。三叔说:“泥鳅很滑,抓时要掐紧些。”游酢不好意思,说:“知道了。”第三只又叉到,三叔说:“再试试。”游酢掐住泥鳅的腹部终于顺利地将它放进竹篓。三叔笑了,说:“行,就这样。” 大约两个时辰,叉了不少泥鳅,叔侄两人开始返回。路上,三叔说:“是动物都有它的弱点,泥鳅虽然滑,但是也有一点点脊梁,掐紧了,它便跑不了。世间的人也有奸猾的,可是也有他的致命要害。你以后出社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如果是奸猾的,得提防着,但是不要怕他。是人总有缺点,抓住要害,他准怕你。” 回到家里,其他人都去睡觉了。三叔说:“我们到吃饭间喝茶,让你三婶忙去。”三婶把泥鳅拿到厨房,倒进木盆里,一只只拿起开肠破肚,杀好、用盐水洗一遍,冷水冲两三遍。锅灶生起火,水烧开后将泥鳅放进锅一烫,用笊篱捞起放在灶台;再抓一大块生姜捣烂,又捣烂两粒蒜头,拿出油罐,用筷子夹出一小块猪肉渣,在锅底转一圈,锅底熬出一点点油气,又将猪肉渣夹回油罐,才将泥鳅放进锅里,撒一点盐花下去,用锅铲翻炒几圈。三婶看泥鳅炒得有六七成熟了,接着生姜、蒜头一齐下,进行大翻炒,一股香气飘进吃饭间。游酢闻到香气,说:“三婶煮得好香啊。”泥鳅炒熟后,她拿了个敞口的碟子装好放在灶台,先洗了两双碗筷和酒杯,送到吃饭间摆放好,又出来将那碟泥鳅端进去,说:“吃不吃得,试试。”游酢说:“肯定好吃,三婶不愧是村里的好厨手。”三婶高兴极了,双手抹了抹胸前的围裙,回答:“定夫,你的嘴真甜。你慢慢吃。”她便回厨房洗锅。三叔从桌角上提起酒壶,先给游酢倒了一杯,再自己满上一杯,说:“这水酒是自家酿的,来,喝一口。”叔侄两人边喝酒边吃泥鳅。三叔说:“种田人吃不起山珍海味,勤劳一点吃些东西不愁没有,泥鳅、鱼、石蚌还是捉得到的。过两天,我去叉几尾鱼,到时节叫你来多喝几杯。”游酢应道:“其实泥鳅、鱼、石蚌这些很好吃,不比那些山珍海味差。”三叔说:“定夫,你年纪不小了,应该讨老婆成个家了。”游酢答道:“叔,我还没有求到功名,等以后再说。”三叔又说:“你到外面闯过,就没有见到好的女子。如果有适合的对象,跟叔说一声。叔帮你去说。”游酢问道:“叔,我们什么时候也去抓石蚌?”石蚌,又名石鸡,山中溪涧栖息的蛙类动物。三叔回答说:“你以为石蚌好抓吗?夜里打着松明火去,爬山的辛苦不说。有的地方石岩坡很陡又滑,爬不好摔下来成肉酱。再说,有时候遇到鬼,迷路了回不来。”游酢听了不再说什么。
两人边说边吃喝,直到泥鳅吃完,才各自回房休息。
入秋后,游复虽然请了好几个医生,病情不见好转,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的书斋再也没法开办,叫人告诉族长。此事在村中引起轩然大波,有儿子在读书的父母都忧愁起来。
几天后村里有个老人去世,大家开始奔到那个家帮忙办丧事。
傍晚,许多乡亲在帮忙做事,有人提到:“老六瘫痪了,咱们村里的孩子到哪里读书呢?” “是啊,孩子们到外村去读书,一来路远,二来极不方便。大些的孩子还可以勉强,可是年龄小的就难办了。” 平时大家没有觉得村里的私塾怎么样,现在经人这么一提,不少人才想到游复的好处。于是,村里人议论纷纷起来。
有的人说,有的人在想,心里都显得很不平静。
忽然,有人说道:“咱们村里不是有质夫、定夫兄弟吗?” “对呀!他们要进京考进士的人,教一些村里的孩子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不知他们愿不愿意。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当先生的收入低,又没有什么出息。” “这也是个问题。他们一心想考出去,将来当大官骑高马,荣华富贵,多么威风,哪里会做教书这种行当。” 有个人说:“哼!考进士那么容易。铁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花。” 另一个插嘴道:“听说铁树千年会开一次花,可是石板就没有听说过会开花呢。” 有人眼尖,远远看见了游醇和游酢身影,轻声地提醒:“嘘——别多嘴啦!” 果然,游醇和游酢来了,听到人们的议论,但是不明白在讲什么,没有吭声就走到人群中去了。
三叔公问游醇道:“下半年咱们村里的孩子没有地方读书,你说怎么办呢?” 游醇看了游酢一眼,温和地回答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三叔公讲:“刚才,村里人说希望你们兄弟能把私塾接着办下去。孩子们就不要到外村去读书。” 游醇沉吟一会儿,回答:“这么大的事情,容我们想一想。” 三叔公说:“那好。我们等你们的回音。” 游醇听了心里想到:自己明年就要去参加考进士出身,如果耽误了前程划不来,要是游酢肯应承就再好不过。
这时,三叔公游正走过来说:“定夫,你大哥他有家庭拖着,你还没有成家,接手最适合。”游酢回答:“叔公,这——”三叔公说:“有什么好想的,你可以边教书边攻读,不会影响了你的前途。读书人的目的,应该就是为天下人办事,《尚书》云:‘天下为公’。凡能够做大事者,无不从小事做起。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何况这是全村人的大事,你掂量、掂量吧。” 当天晚上,游酢回想起进京考试缺钱的情景,觉得自己得为今后进京考试积蓄一点钱,不能再让家里人为难了。不如接受教书这件事,招收一些学生,考得上进士就出去,考不上也有一个谋生的路子。
第二天早晨,他将自己的想法跟父母说了,父母听了很高兴,游潜说:“这样也好。”他去跟堂兄游醇商量,游醇表示:“你的想法很好,我帮你忙。六叔病成那样,他家不适合办学,书斋就借咱们祠堂用一用,桌子和凳子咱们凑一凑。村里有愿意来的都收。” 这天上午,游酢愿意办学的事情定了下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雀跃。
村里几个长辈和管事的人经过商量,书斋按每个学生一年交五十斤谷子,其中每年抽十斤给祖祠做租。晚间,三叔公来将村里人讨论的决定告诉游酢,游酢表示同意。
富垄村虽然不大,不到百人,大多的人家都贫穷,只有几家富户。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多的家庭为没有米下锅犯愁。所以,贫穷人的孩子没有送书斋读书,在家帮忙干活。游酢回忆起自己小时没钱读书的往事,想到:自己接手办学,一定要想办法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读书。
秋后,村中的私塾在游氏祠堂开学了。
报名的这一天上午,来了十几人,有的大人带着,有的小孩子自己来,其中有本族的,也有张、刘、谢、林各姓的。
其他的人报完名都走了,这时游酢发现有个八、九岁的孩子既没有前来报名,也不走。于是,他起身去问那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报名呀?”那孩子回答:“我叫刘全,没有爸爸了,妈妈不让我来读书。”游酢听了,心头一酸,眼泪都快滚落下来,说:“你回去跟妈妈说,你明天就来上课,先生不收你的钱。”刘全点点头,说:“谢谢先生,我就回去跟妈妈讲。” 午饭时,游酢问母亲:“妈,刘全是谁家的孩子?”母亲说:“德本的,他妈妈叫春桃,德本前几年去世,家里只剩母子俩。由于没有了男人,春桃靠给人干活挣点钱度日。怪可怜的。”游酢想起来了,德本是个块头不大的人,很老实,家庭也苦,前些年病故了。
下午,有个家长带着孩子来,问道:“先生,我家里人手紧,孩子来读半天可以吗?”游酢知道农村的特点,他小时候的伙伴就有这样的,因此爽快地回答:“可以。”那家长说:“我这孩子,上午帮别人看牛,下午来书斋读书。这孩子愚,先生辛苦你就是了。”游酢答道:“没问题,你放心。” 可是,游酢发现小时候的同学桂生的儿子已经八岁却没有来报名。
这天傍晚,他就到桂生的家去。太阳下山不久,那玫瑰色的晚霞映照着富垄山村的山水,沿路可以清晰地看见村里的住家以及鸡、鸭的走动,听得见有一两只狗的吠声。
桂生是张家中最穷的一户,住在村尾一座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外面围着篱笆。游酢绕过大半圈篱笆,从中间的篱笆门走进去,看见一群鸡在地面悠悠地走动,忽然一只公鸡“喔喔——”打起鸣来,猪栏里有一只黑糊糊的猪在叫。游酢走进屋里,问道:“有人在家吗?”桂生坐在饭桌的长木凳,他老婆在厨房洗碗筷,桂生见了游酢,连忙站起来,应道:“在,你来啦。”桂生的老婆则放下碗筷转过身用手抹一下围裙,说:“不好意思,屋里又脏又乱。坐吧。”房屋确实不太像样,柱子和墙壁黑咕隆咚的,桌面也蒙着一层黑乎乎的油渍。游酢跟桂生坐了下来,问道:“你儿子呢?”桂生回答:“跑出去玩啦。”游酢说:“你儿子怎么不送去书斋读书?”桂生脸红了,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游酢说:“桂生,你不够意思,咱们俩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桂生的老婆端了一杯茶走出厨房,说:“桂生他不会说话。哦,定夫哥,我是说儿子他还小,过一两年再送去读书。”她将茶递给游酢说:“喝杯茶。”游酢接了茶,说:“嫂子,你不用说,你的家境我了解,我们是兄弟,不会要你的工钱的。看得起我,明天就送儿子去书斋。不行,我自己来带。”桂生和他老婆相互看了看,他老婆应道:“那谢谢你,辛苦你了,明天我送去。”坐着聊了半个多时辰,游酢起身告辞,说:“我还有点事情先回去。你们有空去我家坐坐,明天可一定要将儿子送来啊。”桂生夫妇起身送出门,回答道:“会的。” 第二天早上,桂生的老婆把儿子送来了。游酢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回答:“石头。”游酢听了,问桂生的老婆:“嫂子,孩子几月生的?孩子没有名字怎么行呢?”桂生的老婆回答:“九月初三生的。你给他取一个吧。”游酢听了略思考一下说:“就叫秋阳吧。”桂生的老婆:“好,谢谢你了。我这就回去。”于是,游酢又多了一位学生。
到了傍晚,游酢想起了刘全。他怎么没来呢?放学后,游酢到刘全的家去。
春桃身材中等,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少妇,穿着一身粗布衣杉,她见天色不早正提着一桶猪食去喂猪。游酢走进了院里看见刘全,问道:“刘全,今天怎么不去书斋?”刘全呆住了,眼圈红了,喊道:“妈,先生来了。”春桃笑着走过来,说:“先生不好意思,家里穷,我让他在家里帮忙砍点柴。再过几年,他就长大了。”游酢说:“我也是苦出身的,等十几岁才入书斋,能够体会孩子没有读书的苦处。春桃嫂,你家的情况我知道,让刘全去读书吧。不要酬金,多一个学生没有什么。可是,孩子没有读书就误了他的一生。”春桃犹豫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答:“谢谢先生,以后再看吧。”游酢又说:“春桃嫂,你不让他读书,真的会误了孩子的。”春桃只好回答:“好吧,让我想一想,明天答复你。”游酢见情,说:“不用想,你明天一定得让刘全去读书。”说完走了。
第二天,不见刘全来报名。傍晚,游酢又来到刘全的家。刘全喊道;“妈,先生又来了。”春桃正在屋里擦灶台,听说游酢又来正想躲避,游酢已经迈进门槛,问道:“春桃嫂,忙啥呢?”春桃心虚了,胸口扑扑直跳,嘴上应道:“没啥。”游酢单刀直入地问:“今天刘全怎么没去书斋?”春桃脸红了,胸口跳得更加厉害,支吾着说:“这——”游酢知道她家境,说:“我知道你的难处,刘全用的书、笔,我都准备好了。”春桃很感激,心里想着:他未婚,又年龄跟自己相近,要是不答应,他天天来,如果久了被人说闲话怎么办?于是,便回答:“那——明天让他去。” 第三天早上,刘全果然到了书斋上学。
私塾完全由先生自己掌握,学生有初入学的,只教他读书、识字,有的已经读了两三年,有的读了四五年,文化程度不一,教学课程安排也不一样。还好人少,可以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要求。这对于饱学的年轻游酢来说,可以从容地应付。因此,他可以边教书边自学。
从此,富垄村每天又有了“子曰”、“诗云”的读书声。
在乡村里,有文化的人是很受人敬重的,何况是教书先生呢。从此,除了本族的宗亲依然叫他名字,村里村外其他人见了他都称呼他“游先生”。游潜夫妇和家里的亲人,见游酢能够安定下来教书而欣慰,族里人因为游酢当上了先生也感到脸上有光彩。
游酢想到,自古以来文人都有一个号,因此用家对面的獬豸山为名,自号“豸山”。
父母开始向他提起娶亲的事情,周围的人也陆续有人上门来提亲。游酢的心还想着去拼前途,知道这件事情后,对父母说:“以后再考虑吧。”所以,有人上门来提亲,游潜夫妇只好回答人家:“定夫说,他现在还不想,以后再说。”来提亲的被这样的话挡了回去。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乡村人都明白了,没有人再愿意上门。可是,人们也产生了猜疑和各种风言风语的议论。
一天,村中有个年轻人结婚,几个妇女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像升叔儿子这样的读书人眼光高,说不定想着给皇帝当驸马或者当哪个大官的乘龙快婿呢。”有的说:“难讲啊,误了一春去掉一秋禾,如果不顺的话,以后连二婚的老婆都难娶到。”游酢也去这个家帮忙做事,听到了议论,他知道这事怪不得人家,装着没有听到一样,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大家见他来了,都静了下来。
游醇性格较内向,平时在积极地攻读,准备去参加考试,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也不愿与其他人来往。只有晚间,他才与堂弟游酢交谈学问之事,兄弟俩不时还会因为不同的见解产生辩论。游酌年龄更小,只是边看书边默默地听着两位兄长论长道短。游酢也想静心地学习一点学问,可是责任心强,不但教书的事放不下,而且喜欢交际,人们也爱找他,所以忧乐多多。古云“天道酬勤”,乐善者虽然眼前忙累,到头来自有好报。请君看下回。
五月的一天,游酢去朋友家回来,进门便看见一个国字框脸庞,英气勃勃的十六七岁少年,游醇说:“俗话说来得早,还不如来得巧。”转身问那青年:“猜猜这人是谁?” 那个少年摸摸脑袋,说:“猜不到。” 游醇说:“我介绍一下吧,此人就是鄙人的堂弟,名酢,字定夫。”又向游酢介绍道:“此君姓陈,名灌,字莹中,号了翁,剑州沙县人。你们有缘吧。”陈灌连忙起身拱手道:“久仰、久仰!”,游酢听出陈灌的口音比较生硬,但是还可以辨别出语音的含义,于是回礼道:“彼此、彼此!请坐!” 两人互相问好之后,陈灌问道:“游君青春几何?”游酢谅他年龄相差无几,应道:“皇祐五年的。”陈灌听罢,拱手道:“我小四岁,当称游君为兄矣。”游醇介绍说:“定夫,你不知道,陈君可算得上是一个书香门第、缙缨世家。其远祖陈雍为唐朝御史中丞,本朝有故吏部尚书陈世卿、还有谏议大夫陈称等名宦。”游酢听了拱手道:“贵府确实了得,令人景仰之至。”陈灌心里知道自陈雍迁居固发口以来,陈家可谓人才辈出。可是,他却回答道:“祖上和家族好,不等于我好啊。要是我当乞丐,谁瞧得起?人得靠自己争气。”游酢问道:“陈君的家就在沙县?”,陈灌回答说:“不,在沙县南面两百多里的固发口,俗称‘挂口’。”游醇说:“我有一点事情要办,你们先聊吧。”通过一番交谈,游酢听出了闽北方言与闽西北方言有差别,可是不很大,仔细听还是能够辨得出话意的,如“沙县”一词听起来,听起来像“傻嫌”似的。
于是,两人互相询问了对方的家庭情况、家乡的风土人情。
过了半个多时辰,游醇回来了。三人接着又闲谈了一些读书的事情。
夜有一点深了,游酢知道家里的房间少,游醇已经有妻子和一个儿子,提出说:“大哥,陈君晚上就到我那儿睡。”游醇应道:“好吧。” 这一天夜里,游酢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归宗岩等,陈灌也介绍他家乡栟榈的风景和传说。游酢听了道:“如此神奇之地,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陈灌说:“现在就是机会,以后成了家或者到外面去做事情,就不一定有时间玩。明天叫你哥哥也一起去。”游酢回答道:“目前,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帮忙,下次再说吧。”陈灌听了,说道:“那好,我随时欢迎你去。” 第二天,陈灌便上路回家了。
一连天晴,半个月不见滴雨。白天热得狗直吐舌头,猪在栏里嗷嗷叫;晚上,屋里像炭窑似的。夜间,田野里到处青蛙“贡贡”鸣叫,此起彼伏,乡村的人们不分男女,大多都在自家的坪子上纳凉,人多的场所就听人讲故事。年轻人在家待不住,挑着松明火把出去,有的到田间叉泥鳅,也有的去抓青蛙,到了半夜回来煮了吃;有的则到山林中溪涧抓石蚌。他们大多的是抓来卖钱,到了山中顺着坑沟摸去,希望抓得越多越好,可以卖更多的钱,所以一般都要到天亮才回家,早晨去卖,下午睡觉。
转眼到了六月,游复患病瘫痪在床,书斋只好停了。游醇、游酢听说,连忙前往看望。
游复拉着游醇的手说:“质夫、定夫,你们看我这个样子,你帮忙接手把书斋办下去吧。”游醇犹豫了一下,安慰说:“叔,你先好好养病,也许到了秋天会恢复健康。”游复灰心丧气地说:“我恐怕好不了。”游酢也安慰说:“叔,你身体一向很健,一定会好起来的。” 傍晚时,游酢看见三叔在劈松明,于是问:“晚上去叉泥鳅?”三叔回答说:“是。你要是去,可得把松明火给我点旺旺的。”游酢答道:“听你的。”三叔笑着说:“好,天黑就去。” 天黑后,三叔一手拿着一把铁叉,一手挑着火篓,左肩还背着一个装泥鳅的竹篓,把一只装松明的竹篓递给游酢,说:“走!”游酢接过竹篓背在右肩上,说:“叔,我帮你拿火篓。”三叔说:“不要,等开始要叉泥鳅时,你再帮我抬火篓。”于是,三叔在前,游酢后面跟着。
夏夜很闷热,田野里昆虫在唧唧低鸣,远处传来一阵阵青蛙的鸣叫。虽然是月初,看不见月光,夜空却繁星密集,地面不见一点亮光。在田间走着,游酢问道:“为什么要晚上叉泥鳅?”三叔说:“天气热泥鳅会爬出来歇凉,在田里会留下痕迹,一条条长长的,灯火一照就现出来。照着痕迹叉去,准有的。”他又问:“刚才的田为什么不叉?”三叔应道:“你读书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肥田才有泥鳅。”松明油脂多易燃,走了一段路三叔便给火篓里添一小块松明。到了一份财主的田,三叔把火递给游酢,说:“你和我平肩走,我叫停,你就站住,等我叉完了泥鳅再前进。把鞋脱在这里,回头再穿。下田的时候要看,别把禾苗踩坏了。” 那泥鳅叉是铁的,头部只三四寸长,靠开口约一寸半两边锋利,进去越来越小。泥鳅虽然很滑,一旦被叉住,身体越挣扎就便往刀刃掐得越深。三叔是叉泥鳅的老手,眼尖手快,一下田便叉了一条,提起叉将泥鳅放进竹篓里。叉起第二条时,游酢好奇,说:“叔,我来!”他伸出手要将泥鳅抓出,结果泥鳅一溜掉到田里游走了。三叔说:“泥鳅很滑,抓时要掐紧些。”游酢不好意思,说:“知道了。”第三只又叉到,三叔说:“再试试。”游酢掐住泥鳅的腹部终于顺利地将它放进竹篓。三叔笑了,说:“行,就这样。” 大约两个时辰,叉了不少泥鳅,叔侄两人开始返回。路上,三叔说:“是动物都有它的弱点,泥鳅虽然滑,但是也有一点点脊梁,掐紧了,它便跑不了。世间的人也有奸猾的,可是也有他的致命要害。你以后出社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如果是奸猾的,得提防着,但是不要怕他。是人总有缺点,抓住要害,他准怕你。” 回到家里,其他人都去睡觉了。三叔说:“我们到吃饭间喝茶,让你三婶忙去。”三婶把泥鳅拿到厨房,倒进木盆里,一只只拿起开肠破肚,杀好、用盐水洗一遍,冷水冲两三遍。锅灶生起火,水烧开后将泥鳅放进锅一烫,用笊篱捞起放在灶台;再抓一大块生姜捣烂,又捣烂两粒蒜头,拿出油罐,用筷子夹出一小块猪肉渣,在锅底转一圈,锅底熬出一点点油气,又将猪肉渣夹回油罐,才将泥鳅放进锅里,撒一点盐花下去,用锅铲翻炒几圈。三婶看泥鳅炒得有六七成熟了,接着生姜、蒜头一齐下,进行大翻炒,一股香气飘进吃饭间。游酢闻到香气,说:“三婶煮得好香啊。”泥鳅炒熟后,她拿了个敞口的碟子装好放在灶台,先洗了两双碗筷和酒杯,送到吃饭间摆放好,又出来将那碟泥鳅端进去,说:“吃不吃得,试试。”游酢说:“肯定好吃,三婶不愧是村里的好厨手。”三婶高兴极了,双手抹了抹胸前的围裙,回答:“定夫,你的嘴真甜。你慢慢吃。”她便回厨房洗锅。三叔从桌角上提起酒壶,先给游酢倒了一杯,再自己满上一杯,说:“这水酒是自家酿的,来,喝一口。”叔侄两人边喝酒边吃泥鳅。三叔说:“种田人吃不起山珍海味,勤劳一点吃些东西不愁没有,泥鳅、鱼、石蚌还是捉得到的。过两天,我去叉几尾鱼,到时节叫你来多喝几杯。”游酢应道:“其实泥鳅、鱼、石蚌这些很好吃,不比那些山珍海味差。”三叔说:“定夫,你年纪不小了,应该讨老婆成个家了。”游酢答道:“叔,我还没有求到功名,等以后再说。”三叔又说:“你到外面闯过,就没有见到好的女子。如果有适合的对象,跟叔说一声。叔帮你去说。”游酢问道:“叔,我们什么时候也去抓石蚌?”石蚌,又名石鸡,山中溪涧栖息的蛙类动物。三叔回答说:“你以为石蚌好抓吗?夜里打着松明火去,爬山的辛苦不说。有的地方石岩坡很陡又滑,爬不好摔下来成肉酱。再说,有时候遇到鬼,迷路了回不来。”游酢听了不再说什么。
两人边说边吃喝,直到泥鳅吃完,才各自回房休息。
入秋后,游复虽然请了好几个医生,病情不见好转,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的书斋再也没法开办,叫人告诉族长。此事在村中引起轩然大波,有儿子在读书的父母都忧愁起来。
几天后村里有个老人去世,大家开始奔到那个家帮忙办丧事。
傍晚,许多乡亲在帮忙做事,有人提到:“老六瘫痪了,咱们村里的孩子到哪里读书呢?” “是啊,孩子们到外村去读书,一来路远,二来极不方便。大些的孩子还可以勉强,可是年龄小的就难办了。” 平时大家没有觉得村里的私塾怎么样,现在经人这么一提,不少人才想到游复的好处。于是,村里人议论纷纷起来。
有的人说,有的人在想,心里都显得很不平静。
忽然,有人说道:“咱们村里不是有质夫、定夫兄弟吗?” “对呀!他们要进京考进士的人,教一些村里的孩子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不知他们愿不愿意。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当先生的收入低,又没有什么出息。” “这也是个问题。他们一心想考出去,将来当大官骑高马,荣华富贵,多么威风,哪里会做教书这种行当。” 有个人说:“哼!考进士那么容易。铁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花。” 另一个插嘴道:“听说铁树千年会开一次花,可是石板就没有听说过会开花呢。” 有人眼尖,远远看见了游醇和游酢身影,轻声地提醒:“嘘——别多嘴啦!” 果然,游醇和游酢来了,听到人们的议论,但是不明白在讲什么,没有吭声就走到人群中去了。
三叔公问游醇道:“下半年咱们村里的孩子没有地方读书,你说怎么办呢?” 游醇看了游酢一眼,温和地回答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三叔公讲:“刚才,村里人说希望你们兄弟能把私塾接着办下去。孩子们就不要到外村去读书。” 游醇沉吟一会儿,回答:“这么大的事情,容我们想一想。” 三叔公说:“那好。我们等你们的回音。” 游醇听了心里想到:自己明年就要去参加考进士出身,如果耽误了前程划不来,要是游酢肯应承就再好不过。
这时,三叔公游正走过来说:“定夫,你大哥他有家庭拖着,你还没有成家,接手最适合。”游酢回答:“叔公,这——”三叔公说:“有什么好想的,你可以边教书边攻读,不会影响了你的前途。读书人的目的,应该就是为天下人办事,《尚书》云:‘天下为公’。凡能够做大事者,无不从小事做起。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何况这是全村人的大事,你掂量、掂量吧。” 当天晚上,游酢回想起进京考试缺钱的情景,觉得自己得为今后进京考试积蓄一点钱,不能再让家里人为难了。不如接受教书这件事,招收一些学生,考得上进士就出去,考不上也有一个谋生的路子。
第二天早晨,他将自己的想法跟父母说了,父母听了很高兴,游潜说:“这样也好。”他去跟堂兄游醇商量,游醇表示:“你的想法很好,我帮你忙。六叔病成那样,他家不适合办学,书斋就借咱们祠堂用一用,桌子和凳子咱们凑一凑。村里有愿意来的都收。” 这天上午,游酢愿意办学的事情定了下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雀跃。
村里几个长辈和管事的人经过商量,书斋按每个学生一年交五十斤谷子,其中每年抽十斤给祖祠做租。晚间,三叔公来将村里人讨论的决定告诉游酢,游酢表示同意。
富垄村虽然不大,不到百人,大多的人家都贫穷,只有几家富户。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多的家庭为没有米下锅犯愁。所以,贫穷人的孩子没有送书斋读书,在家帮忙干活。游酢回忆起自己小时没钱读书的往事,想到:自己接手办学,一定要想办法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读书。
秋后,村中的私塾在游氏祠堂开学了。
报名的这一天上午,来了十几人,有的大人带着,有的小孩子自己来,其中有本族的,也有张、刘、谢、林各姓的。
其他的人报完名都走了,这时游酢发现有个八、九岁的孩子既没有前来报名,也不走。于是,他起身去问那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报名呀?”那孩子回答:“我叫刘全,没有爸爸了,妈妈不让我来读书。”游酢听了,心头一酸,眼泪都快滚落下来,说:“你回去跟妈妈说,你明天就来上课,先生不收你的钱。”刘全点点头,说:“谢谢先生,我就回去跟妈妈讲。” 午饭时,游酢问母亲:“妈,刘全是谁家的孩子?”母亲说:“德本的,他妈妈叫春桃,德本前几年去世,家里只剩母子俩。由于没有了男人,春桃靠给人干活挣点钱度日。怪可怜的。”游酢想起来了,德本是个块头不大的人,很老实,家庭也苦,前些年病故了。
下午,有个家长带着孩子来,问道:“先生,我家里人手紧,孩子来读半天可以吗?”游酢知道农村的特点,他小时候的伙伴就有这样的,因此爽快地回答:“可以。”那家长说:“我这孩子,上午帮别人看牛,下午来书斋读书。这孩子愚,先生辛苦你就是了。”游酢答道:“没问题,你放心。” 可是,游酢发现小时候的同学桂生的儿子已经八岁却没有来报名。
这天傍晚,他就到桂生的家去。太阳下山不久,那玫瑰色的晚霞映照着富垄山村的山水,沿路可以清晰地看见村里的住家以及鸡、鸭的走动,听得见有一两只狗的吠声。
桂生是张家中最穷的一户,住在村尾一座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外面围着篱笆。游酢绕过大半圈篱笆,从中间的篱笆门走进去,看见一群鸡在地面悠悠地走动,忽然一只公鸡“喔喔——”打起鸣来,猪栏里有一只黑糊糊的猪在叫。游酢走进屋里,问道:“有人在家吗?”桂生坐在饭桌的长木凳,他老婆在厨房洗碗筷,桂生见了游酢,连忙站起来,应道:“在,你来啦。”桂生的老婆则放下碗筷转过身用手抹一下围裙,说:“不好意思,屋里又脏又乱。坐吧。”房屋确实不太像样,柱子和墙壁黑咕隆咚的,桌面也蒙着一层黑乎乎的油渍。游酢跟桂生坐了下来,问道:“你儿子呢?”桂生回答:“跑出去玩啦。”游酢说:“你儿子怎么不送去书斋读书?”桂生脸红了,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游酢说:“桂生,你不够意思,咱们俩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桂生的老婆端了一杯茶走出厨房,说:“桂生他不会说话。哦,定夫哥,我是说儿子他还小,过一两年再送去读书。”她将茶递给游酢说:“喝杯茶。”游酢接了茶,说:“嫂子,你不用说,你的家境我了解,我们是兄弟,不会要你的工钱的。看得起我,明天就送儿子去书斋。不行,我自己来带。”桂生和他老婆相互看了看,他老婆应道:“那谢谢你,辛苦你了,明天我送去。”坐着聊了半个多时辰,游酢起身告辞,说:“我还有点事情先回去。你们有空去我家坐坐,明天可一定要将儿子送来啊。”桂生夫妇起身送出门,回答道:“会的。” 第二天早上,桂生的老婆把儿子送来了。游酢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回答:“石头。”游酢听了,问桂生的老婆:“嫂子,孩子几月生的?孩子没有名字怎么行呢?”桂生的老婆回答:“九月初三生的。你给他取一个吧。”游酢听了略思考一下说:“就叫秋阳吧。”桂生的老婆:“好,谢谢你了。我这就回去。”于是,游酢又多了一位学生。
到了傍晚,游酢想起了刘全。他怎么没来呢?放学后,游酢到刘全的家去。
春桃身材中等,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少妇,穿着一身粗布衣杉,她见天色不早正提着一桶猪食去喂猪。游酢走进了院里看见刘全,问道:“刘全,今天怎么不去书斋?”刘全呆住了,眼圈红了,喊道:“妈,先生来了。”春桃笑着走过来,说:“先生不好意思,家里穷,我让他在家里帮忙砍点柴。再过几年,他就长大了。”游酢说:“我也是苦出身的,等十几岁才入书斋,能够体会孩子没有读书的苦处。春桃嫂,你家的情况我知道,让刘全去读书吧。不要酬金,多一个学生没有什么。可是,孩子没有读书就误了他的一生。”春桃犹豫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答:“谢谢先生,以后再看吧。”游酢又说:“春桃嫂,你不让他读书,真的会误了孩子的。”春桃只好回答:“好吧,让我想一想,明天答复你。”游酢见情,说:“不用想,你明天一定得让刘全去读书。”说完走了。
第二天,不见刘全来报名。傍晚,游酢又来到刘全的家。刘全喊道;“妈,先生又来了。”春桃正在屋里擦灶台,听说游酢又来正想躲避,游酢已经迈进门槛,问道:“春桃嫂,忙啥呢?”春桃心虚了,胸口扑扑直跳,嘴上应道:“没啥。”游酢单刀直入地问:“今天刘全怎么没去书斋?”春桃脸红了,胸口跳得更加厉害,支吾着说:“这——”游酢知道她家境,说:“我知道你的难处,刘全用的书、笔,我都准备好了。”春桃很感激,心里想着:他未婚,又年龄跟自己相近,要是不答应,他天天来,如果久了被人说闲话怎么办?于是,便回答:“那——明天让他去。” 第三天早上,刘全果然到了书斋上学。
私塾完全由先生自己掌握,学生有初入学的,只教他读书、识字,有的已经读了两三年,有的读了四五年,文化程度不一,教学课程安排也不一样。还好人少,可以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要求。这对于饱学的年轻游酢来说,可以从容地应付。因此,他可以边教书边自学。
从此,富垄村每天又有了“子曰”、“诗云”的读书声。
在乡村里,有文化的人是很受人敬重的,何况是教书先生呢。从此,除了本族的宗亲依然叫他名字,村里村外其他人见了他都称呼他“游先生”。游潜夫妇和家里的亲人,见游酢能够安定下来教书而欣慰,族里人因为游酢当上了先生也感到脸上有光彩。
游酢想到,自古以来文人都有一个号,因此用家对面的獬豸山为名,自号“豸山”。
父母开始向他提起娶亲的事情,周围的人也陆续有人上门来提亲。游酢的心还想着去拼前途,知道这件事情后,对父母说:“以后再考虑吧。”所以,有人上门来提亲,游潜夫妇只好回答人家:“定夫说,他现在还不想,以后再说。”来提亲的被这样的话挡了回去。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乡村人都明白了,没有人再愿意上门。可是,人们也产生了猜疑和各种风言风语的议论。
一天,村中有个年轻人结婚,几个妇女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像升叔儿子这样的读书人眼光高,说不定想着给皇帝当驸马或者当哪个大官的乘龙快婿呢。”有的说:“难讲啊,误了一春去掉一秋禾,如果不顺的话,以后连二婚的老婆都难娶到。”游酢也去这个家帮忙做事,听到了议论,他知道这事怪不得人家,装着没有听到一样,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大家见他来了,都静了下来。
游醇性格较内向,平时在积极地攻读,准备去参加考试,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也不愿与其他人来往。只有晚间,他才与堂弟游酢交谈学问之事,兄弟俩不时还会因为不同的见解产生辩论。游酌年龄更小,只是边看书边默默地听着两位兄长论长道短。游酢也想静心地学习一点学问,可是责任心强,不但教书的事放不下,而且喜欢交际,人们也爱找他,所以忧乐多多。古云“天道酬勤”,乐善者虽然眼前忙累,到头来自有好报。请君看下回。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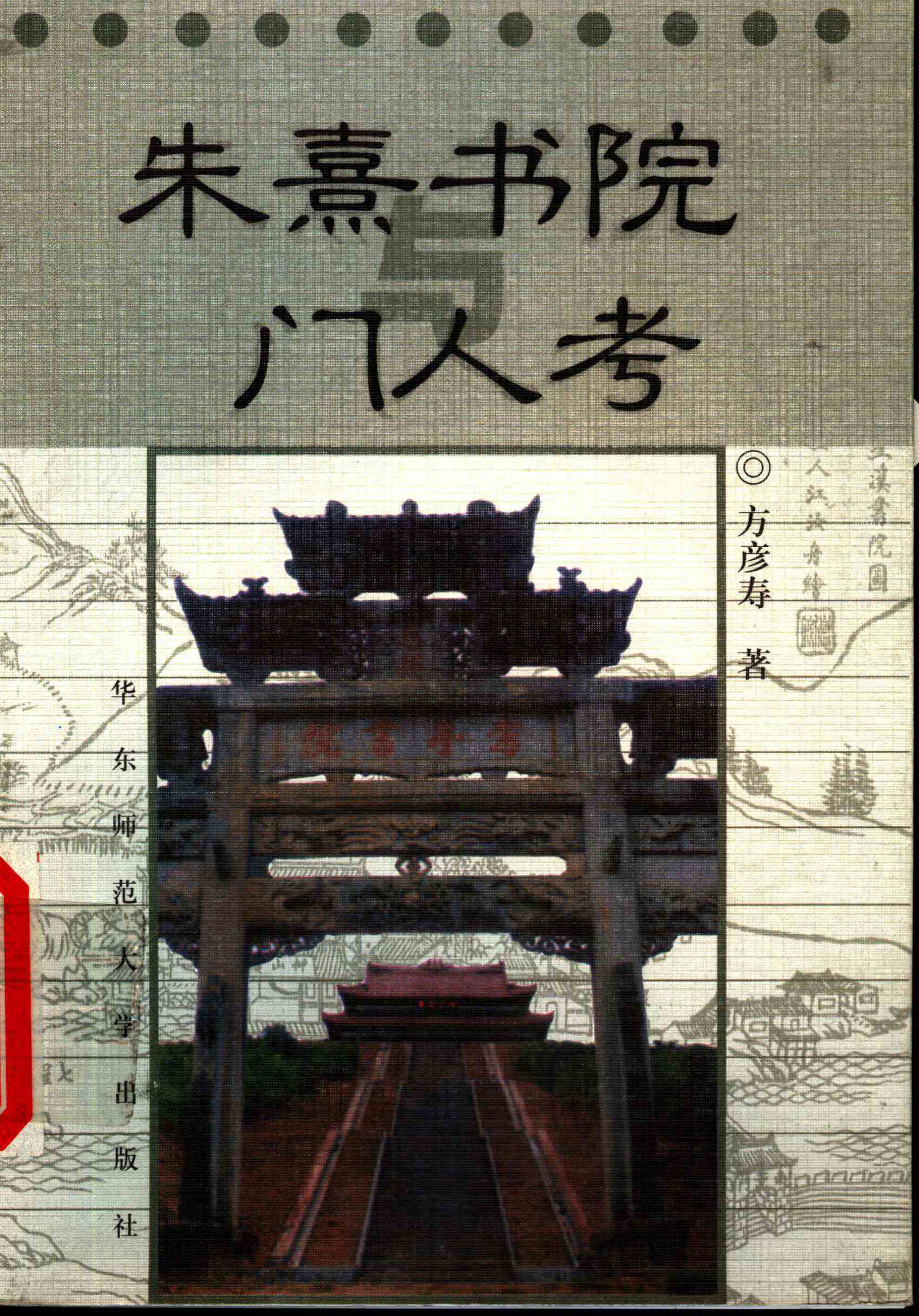
《朱熹书院与门人考》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书院考”和“门人考”两部分,第一部分考证了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六十七所,辨析无关的八所,第二部分考证了朱熹在其创建的四所书院中及门弟子二百七十六人。
阅读
相关人物
游生忠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