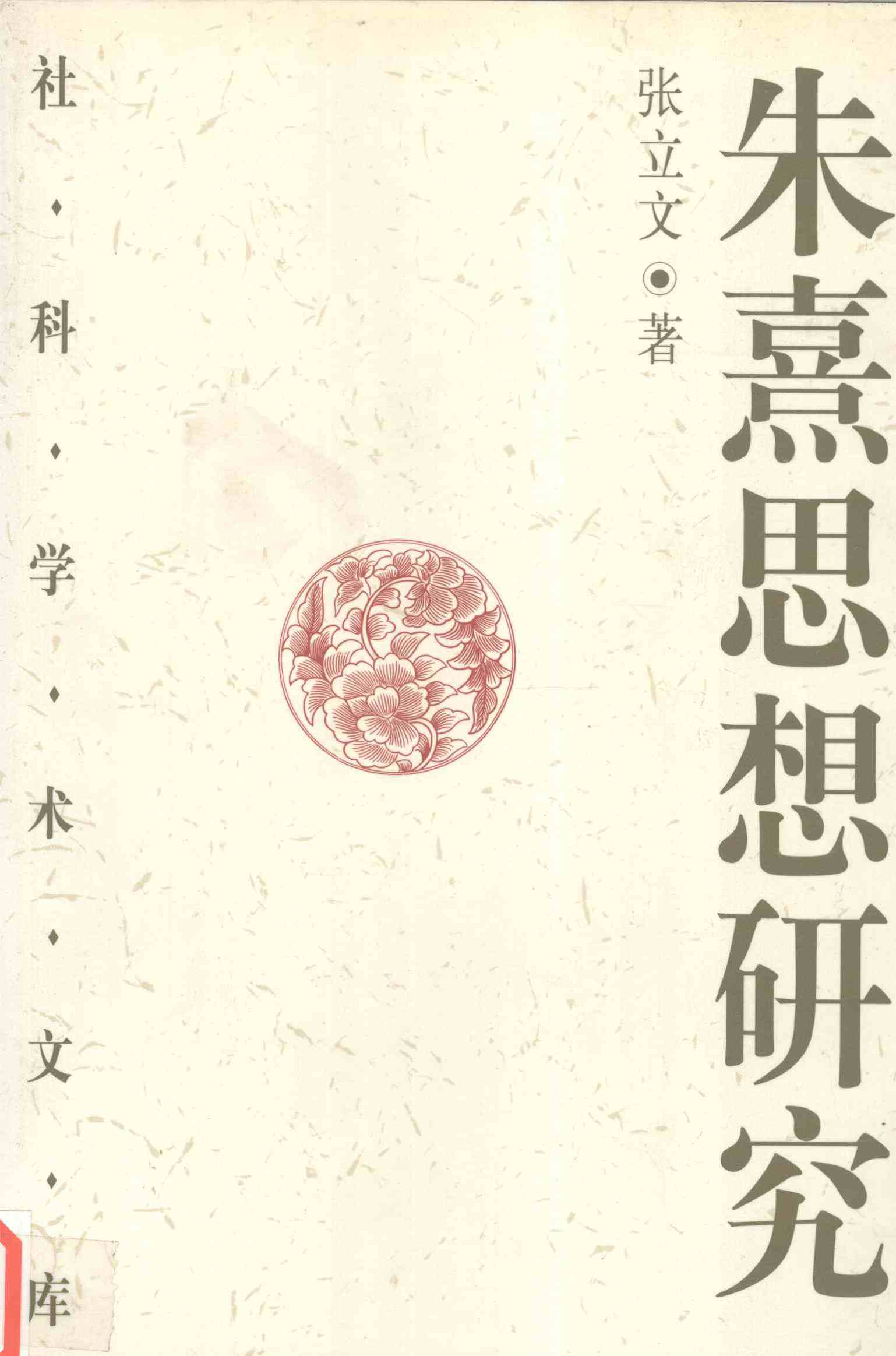内容
我国十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发展,作为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维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理学”,也就转生和形成了。
一、何谓“理学”
“理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理论思维形态,多少年来,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作了种种的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说法,“理学”就是“宋学”,即区别于汉唐以来训诂词章之学的宋代“性命义理”之学,而称之为“宋学”。
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历史朝代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不同的学派,而且也不能揭示“理学”所体现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特点。如果说宋代的“理学”为“宋学”,那么,明代的“理学”,只能称明学。退一步说,若以“性命义理”为“宋学”,虽然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实质,但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界限。作为非主流派的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也谈“性命义理”。叶适说:“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①又说:“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绝殊,乃君子所甚畏也。”②又岂能说他们是主流派理学家!
另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之所以为“道学”,是因为《宋史》立有《道学传》。他们以《道学传》为准,凡列入《道学传》的为理学家,否则就不是理学家。
把《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当时客观事实和各学术派别在理论论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显然没有道破问题的实质。《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负责总编的。他们出于对程、朱的尊崇,只把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只有与程、朱关系极密的邵雍和张栻列入,其他都列入《儒林传》。这本之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明显的例子是对待司马光的问题。朱熹在作《六先生画像赞》时,曾将司马光和周、程、邵、张并提,但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他作《伊洛渊源录》时,将司马光除去,而称“北宋五子”。因此《宋史》编撰者就没有将司马光列入《道学传》。如果放在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中来考察,司马光应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的陆九龄和陆九渊等亦当入《道学传》而无疑。
尽管“道学”这一概念,北宋已有。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程颐也说:“家兄(程颢)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①此处“道学”,并非学派之称,而是指“道”与“学”。朱熹却称二程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②“道学”是指继孔孟往圣之绝学的道统之学。朱熹晚年,政治上遭到排斥,“道学”也受攻击。淳熙十年,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陈贾也说:“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④因此,讲“道学”被视为罪状。朱熹上《封事》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⑤“道学”便是“守道循理”者的称呼。“道学”虽在理宗时被恢复名誉,但到明中叶李贽,抨诋为假道学。后来,道学家或道学先生就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再者也容易与道家之学混淆,因此,“道学”之名被用滥了,超出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之名的特有范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断代哲学史的统称。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没有揭示“理学”的特定的思想实质和特点。如果说“理学”是断代哲学史的统称,那么,它就像清代李威所说的是一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派别统统包容。这样的统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代“道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之名登上历史舞台的。据记载,当时“道学”与反“道学”的论争十分激烈。韩侂胄等以“道学”当名曰“伪学”,由是目“道学”为“伪学”。叶适说:“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①双方论争的阵线也很清楚。尽管当时道学家和反道学家不尽是哲学家,但亦无必要去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既有反“道学”的论争,便有“道学”在,也有非“道学”在。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偏颇。笔者认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学派的总称。
(二)所谓理学
“理学”是北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元旨是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转生,是对于笃守师说的批判,亦是对于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的反动。宋代知识分子起来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实现了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②学术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思潮。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疑六经之首《周易》中的《易传》为非孔子之言;又撰《毛诗本义》,破毛享、郑玄传注。刘敞的《七经小传》,由疑经而改经。此外如司马光、李觏等之疑《孟子》,苏轼之讥《尚书》等,蔚然成风。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①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各个集团、阶层、学派的思想家,依据本集团、阶层、学派的利益及各自的思想,提出了各自救治社会的战略、方案以及主张、学说等。宋王朝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抑兼并,思想上的兼容并蓄和佑文政策,出现一种相对宽松的形势。这种形势为宋代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和生长的气候、土壤,很快形成了宋代各家异说,学派聚奎的可喜情境。
但是思想的解放思潮,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特别是“荆公新法”的失败,学术的论争被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思想上的疑经改经思潮逐渐被无休止的政治党派斗争所冲淡。各派的学说随着政治的起伏而起伏,一时被颁之学官,一时又遭禁受诬,政治风云强烈制约各派学说的发展。原来思想界那种清新的、生气勃勃的空气减弱了;原旨意义上的理学社会思潮,便开始转向了,以至坠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你主观上不愿意参与,客观上亦不可避免。
在庆历至熙宁的二三十年间,先后相继形成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竞艳,相得益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原来“关学”、“洛学”、“新学”、“朔学”、“蜀学”并立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与熙宁新法的失败相联系,元祐初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上台,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为禁学。曾慥的《高斋漫录》说:“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公(王安石)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后来新法派虽又上台执政,但基本上属于政治上的党派斗争,于“新法”本身的发展已无太大关系,这样“新学”便式微了。“蜀学”的苏轼、苏辙,初亦主张改革,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由于方略、方法上的分歧而成为反新法派,在这点上“洛学”和“蜀学”结成了联盟。然而到新法废除后的元祐时期,洛、蜀两派又如同水火。此期间虽互有起伏,但二苏的“蜀学”总因其以三教合一为旨归①,释、道味道较浓而被目为禅。虽然后人有为其辩解的,但终宋之世,未改其“三家为一”的评论。人们虽认为其“三教合一”是“气习之弊”所致,非为邪心,不能像对待王安石“新学”那样贬斥“蜀学”。但又以为其不知“道”,问题也是够严重的了。因此,便将“蜀学”排之于“道学”之外。全祖望囿于宋明理学的正统观念,在《宋元学案》中,将“新学”和“蜀学”摈出正书,附之卷尾。
北宋惟“洛学”独盛,究其因:一是,二程初亦要求变法,后与吕公著、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和“新学”,元祐初,程颐得到他们的推荐,“太皇太后面谕将以为崇政殿说书”。②为哲宗皇帝讲“道学”。由于得太皇太后高氏和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巨公耆儒”的支持和宣扬,“洛学”便得以盛行;二是“洛学”在当时被视为醇儒,而无“蜀学”的那种禅味。程颐在程颢《墓表》中便说,程颢继孟子之后圣人不传之学,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①,因此,得到推崇;三是,门人弟子积极传道,张载死后其高足亦改换门庭,师事程颐。这样不仅“新学”和“蜀学”不能与“洛学”相抗衡,就连“关学”亦无“洛学”那样广泛流传。
南宋初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鉴于北宋时政治斗争强烈左右学术论争之失,而企图从中摆脱出来,进行学术上的创新。他们冷静地总结、发展以往哲学理论思维,朱熹根据其出入佛、道的体会,认为儒学对稳定社会秩序较佛、道有效,绍承孔子、孟子《大学》、《中庸》,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之学之大成,即理学之大成。
所谓“理学”,从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中,可窥其梗概。此书章次的确定,材料的取舍,都体现了“理学”思想精神。共编十四卷:1.道体;2.为学大要;3.格物穷理;4.存养;5.改过迁善,克己复礼;6.齐家之道;7.出处进退辞受之义;8.治国、平天下之道;13.异端之害;14.圣贤气象。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说:“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②作为登“理学”之堂奥,入“理学”之门的书,可谓上乘之作。
朱熹和吕祖谦所概括的这十四个问题,以“道体”和“性”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为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据此,宋明理学的性质和内容,试概括如下:
第一,宋明理学以探讨道体为核心,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本性。这便是理学家所追求的所当然的所以然。所当然即是指自然、社会现象;所以然是指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本体。如“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①。或自然、社会现象之上的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②所当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即道体与自然、社会现象的关系。道体(天理)自身是“寂然不动”的,它“无造作”、“无计度”,然却具有“感而遂通”,或“感应之几”的功能,它是自然、社会现象的终极的根源,即“太极”。
第二,宋明理学以“穷理”为精髓。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后面“道体”(所以然之理)的体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理”(“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之象”之理想人格的自觉,即所谓“脱然有悟处”或“豁然有个觉处”。③“穷理”既是“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亦是“尽性至命”、“寻个是处”④,追求人性的根据。因此,“理有未穷”,知有未尽,“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性”⑤。不能穷得理,就不能尽心尽性。这就是说“穷理”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枢纽,是“明明德”⑥的工夫,所以,后来陆世仪概括说:“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⑦抓住“穷理”这个精髓,便能联结“天人合一”,“己与天为一”。⑧万物与我同体,“物吾与也”,即“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①,达到其乐无穷的“道通为一”的理想境界。
第三,宋明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理学家认为在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凡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理”),是“天理之自然”,或“理之自然”;凡是假的、恶的、丑的、偏的、黑暗的,都是“人欲”,属于该去之列。无论主流派或非主流派都强调义理与大公,排斥功利与私欲。“存天理,去人欲”,便成为当时社会人人必遵而行之的原则。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这就需“主静”、“居敬”的工夫,“涵养须用敬”,周敦颐“仁义中正而主静”,而达到“立人极”。二程“居敬集义”,其宗旨是为明“天理”,“敬”是主一,心不二用;敬是未发之中,发而合乎“中节”;敬是“直内”。如何“居敬”,程颐提出“操存闲邪”和“涵泳存养”两方面的修养方法。从而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
第四,宋明理学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理学家都以此为己任。张载自谓其为学宗旨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程颐述程颢的为学宗旨是:“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③人与天地作为三才,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和社会由于人而有价值,人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这便是“为生民立道”。即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然而,作为“尽性至命”与“孝弟”的融合,“穷神知化”与“礼乐”的融合,把“理”这个普遍的原则与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会通起来,把现实的制度理想化,便是“治国平天下”。
第五,宋明理学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辟佛、老,辨异端。宋明理学家既出佛、老,又融佛、老于儒,从而构筑了与佛、老不同的新的儒学哲学。尽管其间有些思想体系中佛、老的味道浓一些,但又既不等同于佛、老二教,亦不同于一般宗教。理学从根本上说是理性思维,是哲学的思辨。为往圣继绝学,以发扬孔孟学说为职志。通过为学、修德,建构了儒学精神家园,终极关怀,而达“圣贤气象”的境界。
二、理学的思想来源
作为一种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理论思维——哲学,具有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表现为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与先前这方面思想资料、文本的联系。因而必须探讨理学由以转生的思想来源。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形态,它容纳和改铸了先前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资料,并由此出发,建立了理学哲学逻辑结构。
自魏汉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经过长期冲突和融合,为理学的转生准备了思想条件①。理学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生化的观点和佛教的佛性论和思辨哲学,来弥补儒家哲学学说没有严密本体论和心性论体系的缺陷,建立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逻辑结构。
被道教推为教主的老聃,把道(无)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无)是一个“先天地生”的超时空的存在的世界的总根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宇宙生成的图式:“道”(“无”)——“有”(“二、三”)——“万物”。这种道生有的万物化生过程,是哲学家的头脑的虚拟。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理学家提出“道在器先”或“理在气先”的演变脉络。这个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图式,后来几经演变,成为陈抟的《无极图》和《先天图》。据传邵雍的《先天图》,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是从陈抟的《先天图》和《无极图》脱化而来的①。由于周敦颐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与道家宇宙生成、万物生成结合起来,企图从“本然之全体”上建立其哲学逻辑结构,为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走出路子,所以被推为理学的开创者。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等人用道家“道”的自然无为观念,通过对“本末”、“有无”等抽象概念的论证,宣扬一种比“天人感应”、谶纬神学更为思辨化的理性哲学。它对理学的影响有:玄学家关于“本末”、“一多”关系的论证为理学家讲“无极而太极”、“一”与“多”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料;玄学家认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②。万物由于“理”的使然,所以多而不杂乱,众而不迷惑。“理”统摄万物。他说:“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其一也。”①万物依理而存在。从这里可以看到理学家“理在事上”的相承关系;玄学家又特别强调“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千变万化的“有”是现象,本体“无”则是寂然不动的,后来理学家的“主静”说,就是沿着这种思想途径走下来的。
至于佛教的思辨哲学,自隋唐以来,不论是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尽管他们在形式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他们的思辨结构,在本质上有一致之处。在佛教思辨哲学里,“主体”和“本体”原是一个东西,“主体”只是“本体”的幻化。“主体”对于“本体”的体认;实质上也就是“主体”自己回归到自己的本源。“本体”在自身中把自己分二,“本体”则是一个无人身理性,“主体”即是这个无人身理性幻化人身。一般地讲,佛教的思辨哲学,在“本体”安顿自己时,它把世界归结为一个精神本体;但当它把“本体”自己跟自己结合时,它不仅把世界归结为自我意识,而且把自我意识看作与“主体”合而为一的“主体”,“主体”即“本体”。
首先把“理”作为其哲学体系的主要范畴,恐怕要算佛教华严宗了。宗密说:“统惟一真法界,谓总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②“四法界”是: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提出了事与理这一对重要的范畴。所谓“事法界”,就是“一真法界”的心所体现的个别存在;“理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体现的精神本体;“理事无碍”就是互相融通、互不妨碍。华严宗认为,“事”与“理”的关系,事必须依赖理而存在,因为事是虚幻不实的。事虽然形形色色,但不是理的分有,而是理的全体的体现,因为理是不可分割的。华严宗说:“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①既“不可分”,那么,事便是“圆足”的理的体现,因而理是根本的,事为理所显现。理成为华严宗哲学的主要范畴。不过,在华严宗看来,事与理归根到底都是“一心”、“真如”的显现,“理”不也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
对于佛教,理学家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批判佛教与伦理纲常相违戾的方面;二是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与佛教的思辨哲学结合起来。二程总结和吸取了华严宗的思想,提出了“万理归一理”的命题。这样,二程便从“理事无碍法界”中,把“一一事中,理皆全遍”的“万理”归为“一理”,反过来,又把“万理”作为“一理”的显现,经过这样一番改造的工夫以后,“一理”(“理”)就成了宇宙最高的本体。
理学家们都在探索如何吸收佛教思辨哲学,作为儒学家的依据和补充。以佛教天台宗和唯识宗为例,他们思辨哲学的“本体”是“心”和“识”,理学家则是“理”或“心”;在佛教那里本体的安顿自己,使自己表现为“心源”和“真如”,理学家则是“太极”或“良知”;在佛教那里“本体”自己与自己对待,是使“念”(意念)成为自己的对象物和使“识”成为世界的对象物,理学家则使“理”或“心”成为它自身所变现的客体世界的对象物;最后,佛教“本体”自己跟自己的“融合”,即是“止观”和“转识成智”,理学家则是“理”的复归或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不过,当佛教的本体“真如”变异为理学家的本体“理”的时候,它不是佛教的“空寂”的东西,而是囊括了“天地”、“理气”、“道器”、“性命”和伦理道德等实理或“实在”的东西。于是,一个怪异现象出现了:超脱尘世的高僧就转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禅定”的修行就转变成“主静”的修心养性,“观心”的证悟就转变成顿悟的“易简”功夫。理学家思辨哲学的这个特点,显然是隋唐佛教思辨结构的继续和发展。
这种思辨哲学在理学奠基者程颢和程颐那里,就已明显。朱熹则进一步援佛、道入儒,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就在朱熹的同时,理学中的陆九渊“心学”一派就开始转生了,到了明中叶的王守仁,“心学”一派得到进一步发展,王守仁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但从其思辨结构来说,程朱一派则强调了“本体”的安顿,主体与本体的二分,以“理”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就称其为程、朱“理学”;陆、王一派强调了“主体”和“本体”的合一,以“心”为形而上学本原,就称其为陆、王“心学”。如果说,程、朱对佛、道采取“阳违之,阴奉之”的话,那么,陆、王“心学”,便“以心起灭天地”,当时就有人直指“心学”为禅学。
陶宗仪有见于此,而作《三教一源图》①(见第15页图)。
此图不仅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基本范畴的相类和圆通,而且说明了其思辨结构的相类。尽管儒家运用“理”、“性”、“命”,释教使用“戒”、“定”、“慧”,道教使用“精”、“气”、“神”等范畴,但都是通过“健顺”、“阴阳”、“体用”等中介环节,而组成儒、释、道的思想逻辑结构的,并论述了儒、释、道三教归一。但陶说仅见皮毛,而未深入剖析。
戴震通过对佛、道宣扬超然实体的剖析,进一步揭示了“理学”的思想渊源。指出了“三教归一”的状况,揭示了庄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或“神识”作为万物的本体,而程、朱“理学”的所谓“理”,便是从佛、道的“真宰”、“真空”转化来的。“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②“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③“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①老、释“以神为天地之本”,程、朱则“以理为气之本”;老、释“以神为气之主宰”,程、朱则“以理为气之主宰”;老、释“以神能生气”,程、朱则“以理能生气”。总之,“彼别形、神为二本”,“此别理、气为二本”。老、庄、佛教割裂“形、神”为“二本”,然后以“神”为“本”;程、朱割裂“理、气”为“二本”,然后以“理”为“本”。戴震通过比较,说明了“理学”和合儒、佛、道的本来面貌。
理学家除吸收道家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和佛教的佛性论和思辨哲学以外,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也为理学家如何地和合儒、释、道指出了方向。宋代的统治集团,显然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统治集团对儒、释、道所采取的兼容并蓄政策,但随着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统治方式的实行,宋统治集团中对于“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情况,十分头痛,迫切需要寻找一种一统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以“一道德”。①于是,宋初的孙复、石介、李觏等从唐末儒学的复兴中得到启发,他们站在儒家的立场,著文反对佛、道。不过,他们主要是从伦理观点上攻击佛、道,没有超出韩愈排佛的基本论点,未能从哲学上加以批判。在当时思想界引起漪澜水波的是欧阳修的《本论》,他倡导以儒家学说为“本”,佛、道为“邪”。认为对佛、道光从社会经济、伦理观点上去批判还不够,照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也不行,应该“修其本以胜之”②,即倡明儒学,以儒学的礼义来代替对佛、道的信仰。同时,旧儒学在唐代却墨守师说,拘泥训诂,限于名物,已显僵化。它在与佛、道的较量中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简单地倡明儒学显然是不行了。因此,一种以儒学为“本”,和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就应运转生了。
这种儒、释、道三教和合的思潮,与统治者的提倡分不开。宋代统治者不仅基本上沿袭了唐的兼容并蓄的政策,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三次到国子监祭祀文宣王,用一品礼,并立十六戟于孔庙门。同时,他倡导佛教,诏诸路寺院:如在显德二年(后周世宗柴荣年号,公元955年)要废未毁的寺院、已毁而仍存的佛像都保留。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行勤和尚等157人到印度求法;五年,文胜和尚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一百六十卷;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诏天下和尚入殿,试经、律、论三学义十余条,全通者,赐紫衣,号为手表僧。宋太宗赵炅既到国子监谒文宣王,又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度僧尼17万人,大建佛寺,大修佛像。七年(公元982年)建译经院,翻译印度佛经,由天息灾、施护,法天负责。是年令赞宁编《宋高僧传》三十卷。另封华山道士陈抟为“希夷先生”。宋真宗赵恒,亲自到曲阜拜祭孔庙,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他敬佛重道,不仅大译佛经,又应西域和尚法贤之请,作《继圣教序》,放在太宗《圣教序》之后,另作《崇释论》,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并诏令撰《景德传灯录》,一年之内度僧尼23万;而且与道士王钦若伪造“天书”,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召见江西上清县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封为“真静先生”。以龙虎山为“受箓院”,立上清宫,免除田租。还诏令:州郡僧、道犯公罪,可以赎罪。官吏无故毁辱僧尼、道士,要受停职处分,老百姓流放千里。宋徽宗赵佶一方面在孔子庙门增立二十四戟,如王者之制,并亲自写匾“大成殿”,颁赐文庙,书写“先圣殿”,为太学辟雍;另一方面,大力提倡道教,任用道士魏汉律等,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王老志为“洞微先生”,直接参与政治。设道官,立《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道士都给官俸,还宣称自己是“上帝元子太霄帝君下降”,要尊奉他为“教主道君皇帝”。由于三教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宋真宗说:“释道二门,有助世教。”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同时,三教的和合,也孕育着理学的转生。
鲁迅先生指出:“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浑;所谓名儒,做几篇伽兰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①“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②理学家沿着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路子,以儒学为骨干和出发点,否定了佛、道宣扬出世、避世,有碍君臣、父子、夫妇等宗法伦理的形式,而吸收佛、道所宣扬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准则;否定了佛、道要在彼岸世界寻求解脱、成佛、成仙,却吸收了佛、道“禁欲”、“主静”以及思辨哲学的宇宙生成的图式,从而建立了理学哲学逻辑结构。于是,待到“三教同源”机运成熟,理学也就形成了。
三、理学的形成
当然,理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经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到南宋的朱熹集其大成。
唐中叶以后,政治上藩镇割据,国势日蹙;思想上释、道、儒三教鼎立,佛盛儒衰。鉴于此情,一些思想家便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国家。出现了黜佛、道而兴儒学的思潮。这个思潮是以古文运动为其先导的。韩愈和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一扫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体,恢复了先秦和两汉质朴的散文文体,而且使古代哲学获得“新生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恢复了孔子的儒学。由文体的改革运动而引起哲学思想的转型,在历史上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韩愈(公元768—824年)继承了从孔孟到董仲舒的“天命论”,他宣扬“天”能决定人的贵贱福祸,“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①如果得罪了“天”,就要降灾祸或刑罚。
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在于提出了一种儒学“道统”说。他认为“道”是一个精神实体,道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遵守和实行“仁”、“义”的原则就是“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②“道统”传授的谱系,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并以自己续“道统”自诩,开理学家所讲“道统”的先河。对此,朱熹赞赏不已。
韩愈在讲“道统”的时候,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突出地抬高孟子的地位。从秦汉以来,儒学并不特别推崇孟子,《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儒学诸子,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第一卷为《序录》,第二至三十卷分别注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不取《孟子》,为当时《孟子》未列入经典之故。韩愈却认为孟子独得孔子之正传,他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③视孟子为诸子之上。二是尊崇《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朱熹认为,汉魏以来,它不被人所重视,韩愈在《原道》中开始强调《大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才逐渐被人所重视。他是这样说的:“《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弟,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①韩愈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应该从“诚意”做起,而达到“治国”、“平天下”。《孟子》、《大学》为理学家所特别崇奉,实自韩愈开其端。韩愈从当时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动摇中,使儒家学说重新抬头,他对儒家学说重新做了诠释和阐发,无疑受到后来理学家的重视。
李翱(公元772—841年)的思想却渗透了佛教的义理。韩愈在讲“性三品”的时候,提到“性”与“情”的关系,然他没有说清楚“善恶”的来源问题。李翱融合佛教的“有情有性”、“无情有性”的佛性论与儒家的心性论,而作《复性书》三篇,发挥孟子的“性善说”。他依据子思的《中庸》②,来说明“恶”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了“性善情恶”说。他说:水本来是清的,泥沙把水弄浑了,泥沙沉淀,水就恢复了清;“性”本是“善”的,喜、怒、哀、惧等“情”把“性”昏蔽了。去掉“情”,就能恢复“善性”③。其实,李翱所讲的“性”,相当于佛教所讲的“本心”,“佛性”;这里所讲的“情”,则相当于佛教的“无明”,“烦恼”。佛教认为,人的本心是“净明圆觉”的,它为“无明”、“烦恼”所昏蔽。因此,去掉“无明”、“烦恼”,便能发明“本心。”
怎样复性呢?李翱认为,先要做到“不虑不思”,然后才能做到“不动心”,即要使“心”处于绝对静止状态,不受丝毫外物的引诱。这种使心进到“寂然不动”的境界,就是《中庸》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时“中”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情欲”就不会发生,也就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他要求通过什么也不想,即禅宗所谓“无念为宗”,来消除心中一切“情欲”杂念,以恢复“善性”,达到精神的绝对超脱,就能与宇宙合一,万物也与我“休作与共”①,通而为一②。
李翱援佛入儒,他的《复性书》简言之,可说是具体而微的理学著作。因此,大得朱熹称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他大谈“性命义理”,“性善情恶”说,把“性”与“情”分别开来。认为“性”是“天”所命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③开启了理学家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先河;第二,他的“弗虑弗思”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即是道学家的所谓“主敬”,是后来理学家争论《中庸》里“未发”、“已发”的先声;第三,他把《中庸》里所讲的“性命之学”,看作是孔孟学说的精髓,因此特别推崇《中庸》。
自秦汉以来,《中庸》也与《大学》一样,并不被人们特别重视,经韩愈和李翱的表彰,后来理学家又纷纷作注解,便取得了与《论语》、《孟子》相当的地位,从而称为《四书》。被看作“六经的阶梯”,都成了儒家的经典。
从提倡儒家“道统”和“性情说”来讲,韩愈和李翱可说是“理学”的先驱。但是,朱熹并不承认。他在编《伊洛渊源录》时,根本不提韩愈和李翱,而把周敦颐捧为理学的开创者,因此,他的学生在《朱子语类》中,把周、程和孔、孟列为一卷,而与《战国汉唐诸子》分开。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异致,然在如何复兴儒学的方法、理路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韩愈以孔子之道为准则,排斥一切,以维护儒家圣贤一脉相传的“道统”。在形式上他似乎捍卫了儒家思想的纯洁性,但他没有根据社会需要的发展而发展儒学,实际上是窒息了儒学。韩愈激烈排斥佛教,主要仍着眼于伦常、费财、夷狄、伤风败俗等老问题,而于佛道思辨哲学几乎未触及。即没有从“本然之全体”上批判佛、道。苏子由评论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①不知形而上的哲学理论问题,这便是韩愈的儒学之所以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症结所在。
柳宗元以孔子之道为准绳,采取有容乃大、吐纳百家的开放方法。他认为儒、佛是可通同、可调和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②这个“合”,是指佛、儒相通之处,这在柳宗元看来,是属于“伸所长”的范围,而佛教的“迹”,是他所黜的“奇袤”。于是,他批评韩愈由于不入佛,而不能区别佛教的“迹”与内容,“外”与“中”之弊。
宋明理学家在总结以往儒释论争的经验教训时,深感韩愈封闭的、简单的方法之弊,而采取了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他们均沿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走出入佛、道的和合途径。
韩、柳都讲“道”,然而韩、柳“道”的内涵和侧重点是不同的。韩愈强调《大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以“正心诚意”来与佛、老相抗衡,而不讲“致知格物”,即不及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被朱熹批评为“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③可谓击中要害。柳宗元与韩愈的分歧便在于此。柳宗元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是“道”。“道”既是自然现象亦是社会现象的概括和抽象。“道”不离“器”,“道”以物为准,依物而存,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道”。“人道”的旨趣在于“利人”、“备事”。而不讲“天”与“神”。所谓“天道”,就是指自然及其规律。如果“道德”是就“人道”而言,则“阴阳”是就“天道”说的。“天道”的具体内容便是“阴阳之气”或称“元气”。
柳宗元的哲学逻辑结构是:
两宋理学家讲道、行道,被认为是重要课题。道学盛于宋,而实萌于韩、柳。然而,韩愈比较偏重伦理道德,而柳宗元合天地自然和社会伦理为一的道学思想体系,对理学家构筑融自然、社会、人类为一的思想体系,影响更深远。
如果说韩愈在建立“道”的学说中,注重《大学》,李翱强调《中庸》,对宋明理学家有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柳宗元重视《周易》,在他的文章中,对《周易》思想顺手拈来,非常贴切而言,对宋明理学家亦有重要影响。理学家讲《易》著《易》,易学逻辑结构几乎是他们思想体系的圭臬。
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韩愈与柳宗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讨论了“天人”关系问题。柳宗元针对韩愈的“天”能赏善罚恶说,明确指出:天地、元气、阴阳如同果蓏、痈痔、草木,都是没有意志,不知报、怒,不会赏、罚的自然物。人事的功、祸与上天无关,是人自己造成的,“非天预乎人也”。这六个字是柳宗元对刘禹锡《天论》三篇的概括。当时刘禹锡鉴于柳宗元《天说》是“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①。把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发展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辨关系。宋明理学家很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并围绕天人关系而扩展为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心与物等问题,使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理学家一方面否定了韩愈天是能赏善罚恶的主宰之天。以“天”为宇宙或自然界,而与柳宗元相通。另一方面,理学家否定了韩愈人为天地之“疣赘”的观点。在韩愈的“天人关系”中,天是主宰,人是天的奴仆,完全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理学家把“人”从“天”的奴役下解脱出来,赋予人以应有的地位,并以人为中心,说明天人关系,而与柳、刘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相接近。
柳宗元在提出天人“不相予”的同时,亦提出了“元气自动”论。他认为,渺茫宇宙的本始,昼夜明暗的交替,天地万物的造始、发展,都是元气的运动变化,天地万物是“元气”的表现形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学说,对后来宋明理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韩愈着重在纲常和道统论方面,那么柳宗元着重在“统合儒释”的思维路径上,以及天人关系、“元气自动”论方面,实开宋明理学学说之先河。柳宗元入佛、道而出佛、道,企图建立一个能融会“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原望,由于宋明理学的转生而完成了。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做知府时,程颢、程颐拜他为师②。他既受佛教影响,曾领教过润州鹤林寺的寿涯,南昌黄龙山的慧南和祖心,庐山归宗寺的了元;又授道入儒,改造道教宇宙生成论,描绘了一个世界生成、发展的《太极图》。从人物的化生到成男成女,都是从这个图式中推演出
动静 变合 妙凝 交感来的。从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演化过程。《太极图》及其《太极图说》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毛奇龄曾说,《太极图说》其中有些说法“直用其(宗密)语”①,是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周敦颐继承李翱,发挥《中庸》里诚的观念,把诚说成是超然的万物本原。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②他还发挥《中庸》中“致中和”作为诚的修养方法。如何达到中?他认为要主静。所谓主静,即是无欲③。“无欲”就达到了“诚立明通”的立人极境界。周敦颐儒学化了的《太极图说》给理学家援佛、道入儒以启示。因此,朱熹称赞周敦颐“闻道甚早”④,“看得这理熟,纵横妙用,只是这数个字,都括尽了。”⑤这大概是朱熹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创者的原因。
邵雍(公元1011—1077年)与周敦颐一样,出入于释、老,而反求诸《六经》。他的《先天图》与周敦颐的《太极图》都来自道教,与邵雍交往甚密的程颢曾说:邵雍之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⑥。《宋史·邵雍传》说:“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显然邵雍问学道教中人李之才,从“本然之全本”上建立其宇宙观。但他并不囿于道教,他的目的是援道入儒,复兴儒学。
他把道教的宇宙生成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吾”融合起来,从心中推衍出宇宙万物。他说:“物有声色气味,人有耳目口鼻。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①物有声、色、气、味,那是人的耳、目、口、鼻等感觉的结果。因而反观内求,什么都具备了。朱熹继承了邵雍的“象数学”及其“一分为二”的思想。邵雍把由“太极”到万物的生成过程,看成是“一分为二”的过程。经朱熹继承和发挥在哲学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张载(公元1020—1077年)继承和发展了柳宗元的思想。
其一,“惟元气存”。即把气作为世界万物多样性的统一基础,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观点。构筑了气本论的哲学逻辑结构。
其二,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从而提出运动变化的泉源是“气”内部的冲突性。“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②的思想。
其三,元气运动变化的形式是相互“交错”。张载将柳宗元的“交错”改造为“交感”。阴阳二端相感,是天地间的普遍现象。
理学的另一奠基者是程颢(公元1032—1085年)和程颐(公元1033—1107年)二程沿着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路子,以儒学为核心,吸收儒家很少讲到而佛、道所津津乐道的宇宙构成、万物化成问题以及其思辨哲学,建立了理本论哲学逻辑结构。正如程颢所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二程把他们体贴出来的“天理”(“理”)作为世界万物的终极根据,可说是受佛教三论宗、华严宗的启发。尽管先秦以来《孟子》、《周易·系辞传》都讲到“理”,但没有作为其哲学的形上学范畴,惟独二程把“理”提升为宇宙的根据。在二程的心目中,“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又是社会的最高原则,并体现为“三纲五常”。①北宋社会要求哲学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作出系统地回答。二程适应了这种需要,他们融合三教,把自然观、体认论、价值观、人性论、道德论、工夫论等各方面问题统统纳入理学体系,提出了“理气”、“道器”、“形而上形而下”、“格物致知”、“天理人欲”、“道心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等一系列理学家所讨论不休的问题,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因而,二程深得朱熹推崇。朱熹认为,孔子死后,得“圣人”之心传的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直到二程出来,“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②,所谓圣人的心传祕旨才又续了下来。所以,他说:“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③把个二程与孔、孟并提。有时,朱熹甚至把程颢比为颜渊,程颐比之孟子,“明道可比颜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处,然伊川收束检制处,孟子却不能到。”④这就是说,孟子与程颐各有千秋,譬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⑤把二程抬到很高的地位。
宋明理学由于二程建立了理本论的哲学逻辑结构和张载建立了气本论的哲学逻辑结构,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朱熹吸收二程的“理”作为其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又改造张载的气作为“理”返回到“物”的中介,起着沟通理与物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而建立了哲学逻辑结构。
总之,理学的转生和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是北宋初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冲突的化解;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而和合结晶;是重建道德形上学的需要;是社会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智慧。
一、何谓“理学”
“理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理论思维形态,多少年来,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作了种种的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说法,“理学”就是“宋学”,即区别于汉唐以来训诂词章之学的宋代“性命义理”之学,而称之为“宋学”。
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历史朝代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不同的学派,而且也不能揭示“理学”所体现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特点。如果说宋代的“理学”为“宋学”,那么,明代的“理学”,只能称明学。退一步说,若以“性命义理”为“宋学”,虽然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实质,但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界限。作为非主流派的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也谈“性命义理”。叶适说:“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①又说:“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绝殊,乃君子所甚畏也。”②又岂能说他们是主流派理学家!
另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之所以为“道学”,是因为《宋史》立有《道学传》。他们以《道学传》为准,凡列入《道学传》的为理学家,否则就不是理学家。
把《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当时客观事实和各学术派别在理论论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显然没有道破问题的实质。《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负责总编的。他们出于对程、朱的尊崇,只把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只有与程、朱关系极密的邵雍和张栻列入,其他都列入《儒林传》。这本之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明显的例子是对待司马光的问题。朱熹在作《六先生画像赞》时,曾将司马光和周、程、邵、张并提,但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他作《伊洛渊源录》时,将司马光除去,而称“北宋五子”。因此《宋史》编撰者就没有将司马光列入《道学传》。如果放在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中来考察,司马光应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的陆九龄和陆九渊等亦当入《道学传》而无疑。
尽管“道学”这一概念,北宋已有。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程颐也说:“家兄(程颢)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①此处“道学”,并非学派之称,而是指“道”与“学”。朱熹却称二程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②“道学”是指继孔孟往圣之绝学的道统之学。朱熹晚年,政治上遭到排斥,“道学”也受攻击。淳熙十年,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陈贾也说:“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④因此,讲“道学”被视为罪状。朱熹上《封事》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⑤“道学”便是“守道循理”者的称呼。“道学”虽在理宗时被恢复名誉,但到明中叶李贽,抨诋为假道学。后来,道学家或道学先生就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再者也容易与道家之学混淆,因此,“道学”之名被用滥了,超出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之名的特有范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断代哲学史的统称。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没有揭示“理学”的特定的思想实质和特点。如果说“理学”是断代哲学史的统称,那么,它就像清代李威所说的是一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派别统统包容。这样的统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代“道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之名登上历史舞台的。据记载,当时“道学”与反“道学”的论争十分激烈。韩侂胄等以“道学”当名曰“伪学”,由是目“道学”为“伪学”。叶适说:“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①双方论争的阵线也很清楚。尽管当时道学家和反道学家不尽是哲学家,但亦无必要去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既有反“道学”的论争,便有“道学”在,也有非“道学”在。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偏颇。笔者认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学派的总称。
(二)所谓理学
“理学”是北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元旨是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转生,是对于笃守师说的批判,亦是对于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的反动。宋代知识分子起来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实现了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②学术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思潮。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疑六经之首《周易》中的《易传》为非孔子之言;又撰《毛诗本义》,破毛享、郑玄传注。刘敞的《七经小传》,由疑经而改经。此外如司马光、李觏等之疑《孟子》,苏轼之讥《尚书》等,蔚然成风。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①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各个集团、阶层、学派的思想家,依据本集团、阶层、学派的利益及各自的思想,提出了各自救治社会的战略、方案以及主张、学说等。宋王朝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抑兼并,思想上的兼容并蓄和佑文政策,出现一种相对宽松的形势。这种形势为宋代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和生长的气候、土壤,很快形成了宋代各家异说,学派聚奎的可喜情境。
但是思想的解放思潮,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特别是“荆公新法”的失败,学术的论争被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思想上的疑经改经思潮逐渐被无休止的政治党派斗争所冲淡。各派的学说随着政治的起伏而起伏,一时被颁之学官,一时又遭禁受诬,政治风云强烈制约各派学说的发展。原来思想界那种清新的、生气勃勃的空气减弱了;原旨意义上的理学社会思潮,便开始转向了,以至坠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你主观上不愿意参与,客观上亦不可避免。
在庆历至熙宁的二三十年间,先后相继形成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竞艳,相得益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原来“关学”、“洛学”、“新学”、“朔学”、“蜀学”并立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与熙宁新法的失败相联系,元祐初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上台,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为禁学。曾慥的《高斋漫录》说:“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公(王安石)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后来新法派虽又上台执政,但基本上属于政治上的党派斗争,于“新法”本身的发展已无太大关系,这样“新学”便式微了。“蜀学”的苏轼、苏辙,初亦主张改革,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由于方略、方法上的分歧而成为反新法派,在这点上“洛学”和“蜀学”结成了联盟。然而到新法废除后的元祐时期,洛、蜀两派又如同水火。此期间虽互有起伏,但二苏的“蜀学”总因其以三教合一为旨归①,释、道味道较浓而被目为禅。虽然后人有为其辩解的,但终宋之世,未改其“三家为一”的评论。人们虽认为其“三教合一”是“气习之弊”所致,非为邪心,不能像对待王安石“新学”那样贬斥“蜀学”。但又以为其不知“道”,问题也是够严重的了。因此,便将“蜀学”排之于“道学”之外。全祖望囿于宋明理学的正统观念,在《宋元学案》中,将“新学”和“蜀学”摈出正书,附之卷尾。
北宋惟“洛学”独盛,究其因:一是,二程初亦要求变法,后与吕公著、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和“新学”,元祐初,程颐得到他们的推荐,“太皇太后面谕将以为崇政殿说书”。②为哲宗皇帝讲“道学”。由于得太皇太后高氏和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巨公耆儒”的支持和宣扬,“洛学”便得以盛行;二是“洛学”在当时被视为醇儒,而无“蜀学”的那种禅味。程颐在程颢《墓表》中便说,程颢继孟子之后圣人不传之学,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①,因此,得到推崇;三是,门人弟子积极传道,张载死后其高足亦改换门庭,师事程颐。这样不仅“新学”和“蜀学”不能与“洛学”相抗衡,就连“关学”亦无“洛学”那样广泛流传。
南宋初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鉴于北宋时政治斗争强烈左右学术论争之失,而企图从中摆脱出来,进行学术上的创新。他们冷静地总结、发展以往哲学理论思维,朱熹根据其出入佛、道的体会,认为儒学对稳定社会秩序较佛、道有效,绍承孔子、孟子《大学》、《中庸》,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之学之大成,即理学之大成。
所谓“理学”,从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中,可窥其梗概。此书章次的确定,材料的取舍,都体现了“理学”思想精神。共编十四卷:1.道体;2.为学大要;3.格物穷理;4.存养;5.改过迁善,克己复礼;6.齐家之道;7.出处进退辞受之义;8.治国、平天下之道;13.异端之害;14.圣贤气象。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说:“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②作为登“理学”之堂奥,入“理学”之门的书,可谓上乘之作。
朱熹和吕祖谦所概括的这十四个问题,以“道体”和“性”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为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据此,宋明理学的性质和内容,试概括如下:
第一,宋明理学以探讨道体为核心,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本性。这便是理学家所追求的所当然的所以然。所当然即是指自然、社会现象;所以然是指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本体。如“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①。或自然、社会现象之上的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②所当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即道体与自然、社会现象的关系。道体(天理)自身是“寂然不动”的,它“无造作”、“无计度”,然却具有“感而遂通”,或“感应之几”的功能,它是自然、社会现象的终极的根源,即“太极”。
第二,宋明理学以“穷理”为精髓。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后面“道体”(所以然之理)的体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理”(“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之象”之理想人格的自觉,即所谓“脱然有悟处”或“豁然有个觉处”。③“穷理”既是“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亦是“尽性至命”、“寻个是处”④,追求人性的根据。因此,“理有未穷”,知有未尽,“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性”⑤。不能穷得理,就不能尽心尽性。这就是说“穷理”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枢纽,是“明明德”⑥的工夫,所以,后来陆世仪概括说:“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⑦抓住“穷理”这个精髓,便能联结“天人合一”,“己与天为一”。⑧万物与我同体,“物吾与也”,即“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①,达到其乐无穷的“道通为一”的理想境界。
第三,宋明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理学家认为在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凡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理”),是“天理之自然”,或“理之自然”;凡是假的、恶的、丑的、偏的、黑暗的,都是“人欲”,属于该去之列。无论主流派或非主流派都强调义理与大公,排斥功利与私欲。“存天理,去人欲”,便成为当时社会人人必遵而行之的原则。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这就需“主静”、“居敬”的工夫,“涵养须用敬”,周敦颐“仁义中正而主静”,而达到“立人极”。二程“居敬集义”,其宗旨是为明“天理”,“敬”是主一,心不二用;敬是未发之中,发而合乎“中节”;敬是“直内”。如何“居敬”,程颐提出“操存闲邪”和“涵泳存养”两方面的修养方法。从而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
第四,宋明理学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理学家都以此为己任。张载自谓其为学宗旨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程颐述程颢的为学宗旨是:“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③人与天地作为三才,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和社会由于人而有价值,人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这便是“为生民立道”。即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然而,作为“尽性至命”与“孝弟”的融合,“穷神知化”与“礼乐”的融合,把“理”这个普遍的原则与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会通起来,把现实的制度理想化,便是“治国平天下”。
第五,宋明理学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辟佛、老,辨异端。宋明理学家既出佛、老,又融佛、老于儒,从而构筑了与佛、老不同的新的儒学哲学。尽管其间有些思想体系中佛、老的味道浓一些,但又既不等同于佛、老二教,亦不同于一般宗教。理学从根本上说是理性思维,是哲学的思辨。为往圣继绝学,以发扬孔孟学说为职志。通过为学、修德,建构了儒学精神家园,终极关怀,而达“圣贤气象”的境界。
二、理学的思想来源
作为一种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理论思维——哲学,具有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表现为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与先前这方面思想资料、文本的联系。因而必须探讨理学由以转生的思想来源。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形态,它容纳和改铸了先前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资料,并由此出发,建立了理学哲学逻辑结构。
自魏汉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经过长期冲突和融合,为理学的转生准备了思想条件①。理学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生化的观点和佛教的佛性论和思辨哲学,来弥补儒家哲学学说没有严密本体论和心性论体系的缺陷,建立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逻辑结构。
被道教推为教主的老聃,把道(无)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无)是一个“先天地生”的超时空的存在的世界的总根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宇宙生成的图式:“道”(“无”)——“有”(“二、三”)——“万物”。这种道生有的万物化生过程,是哲学家的头脑的虚拟。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理学家提出“道在器先”或“理在气先”的演变脉络。这个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图式,后来几经演变,成为陈抟的《无极图》和《先天图》。据传邵雍的《先天图》,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是从陈抟的《先天图》和《无极图》脱化而来的①。由于周敦颐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与道家宇宙生成、万物生成结合起来,企图从“本然之全体”上建立其哲学逻辑结构,为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走出路子,所以被推为理学的开创者。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等人用道家“道”的自然无为观念,通过对“本末”、“有无”等抽象概念的论证,宣扬一种比“天人感应”、谶纬神学更为思辨化的理性哲学。它对理学的影响有:玄学家关于“本末”、“一多”关系的论证为理学家讲“无极而太极”、“一”与“多”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料;玄学家认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②。万物由于“理”的使然,所以多而不杂乱,众而不迷惑。“理”统摄万物。他说:“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其一也。”①万物依理而存在。从这里可以看到理学家“理在事上”的相承关系;玄学家又特别强调“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千变万化的“有”是现象,本体“无”则是寂然不动的,后来理学家的“主静”说,就是沿着这种思想途径走下来的。
至于佛教的思辨哲学,自隋唐以来,不论是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尽管他们在形式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他们的思辨结构,在本质上有一致之处。在佛教思辨哲学里,“主体”和“本体”原是一个东西,“主体”只是“本体”的幻化。“主体”对于“本体”的体认;实质上也就是“主体”自己回归到自己的本源。“本体”在自身中把自己分二,“本体”则是一个无人身理性,“主体”即是这个无人身理性幻化人身。一般地讲,佛教的思辨哲学,在“本体”安顿自己时,它把世界归结为一个精神本体;但当它把“本体”自己跟自己结合时,它不仅把世界归结为自我意识,而且把自我意识看作与“主体”合而为一的“主体”,“主体”即“本体”。
首先把“理”作为其哲学体系的主要范畴,恐怕要算佛教华严宗了。宗密说:“统惟一真法界,谓总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②“四法界”是: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提出了事与理这一对重要的范畴。所谓“事法界”,就是“一真法界”的心所体现的个别存在;“理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体现的精神本体;“理事无碍”就是互相融通、互不妨碍。华严宗认为,“事”与“理”的关系,事必须依赖理而存在,因为事是虚幻不实的。事虽然形形色色,但不是理的分有,而是理的全体的体现,因为理是不可分割的。华严宗说:“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①既“不可分”,那么,事便是“圆足”的理的体现,因而理是根本的,事为理所显现。理成为华严宗哲学的主要范畴。不过,在华严宗看来,事与理归根到底都是“一心”、“真如”的显现,“理”不也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
对于佛教,理学家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批判佛教与伦理纲常相违戾的方面;二是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与佛教的思辨哲学结合起来。二程总结和吸取了华严宗的思想,提出了“万理归一理”的命题。这样,二程便从“理事无碍法界”中,把“一一事中,理皆全遍”的“万理”归为“一理”,反过来,又把“万理”作为“一理”的显现,经过这样一番改造的工夫以后,“一理”(“理”)就成了宇宙最高的本体。
理学家们都在探索如何吸收佛教思辨哲学,作为儒学家的依据和补充。以佛教天台宗和唯识宗为例,他们思辨哲学的“本体”是“心”和“识”,理学家则是“理”或“心”;在佛教那里本体的安顿自己,使自己表现为“心源”和“真如”,理学家则是“太极”或“良知”;在佛教那里“本体”自己与自己对待,是使“念”(意念)成为自己的对象物和使“识”成为世界的对象物,理学家则使“理”或“心”成为它自身所变现的客体世界的对象物;最后,佛教“本体”自己跟自己的“融合”,即是“止观”和“转识成智”,理学家则是“理”的复归或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不过,当佛教的本体“真如”变异为理学家的本体“理”的时候,它不是佛教的“空寂”的东西,而是囊括了“天地”、“理气”、“道器”、“性命”和伦理道德等实理或“实在”的东西。于是,一个怪异现象出现了:超脱尘世的高僧就转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禅定”的修行就转变成“主静”的修心养性,“观心”的证悟就转变成顿悟的“易简”功夫。理学家思辨哲学的这个特点,显然是隋唐佛教思辨结构的继续和发展。
这种思辨哲学在理学奠基者程颢和程颐那里,就已明显。朱熹则进一步援佛、道入儒,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就在朱熹的同时,理学中的陆九渊“心学”一派就开始转生了,到了明中叶的王守仁,“心学”一派得到进一步发展,王守仁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但从其思辨结构来说,程朱一派则强调了“本体”的安顿,主体与本体的二分,以“理”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就称其为程、朱“理学”;陆、王一派强调了“主体”和“本体”的合一,以“心”为形而上学本原,就称其为陆、王“心学”。如果说,程、朱对佛、道采取“阳违之,阴奉之”的话,那么,陆、王“心学”,便“以心起灭天地”,当时就有人直指“心学”为禅学。
陶宗仪有见于此,而作《三教一源图》①(见第15页图)。
此图不仅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基本范畴的相类和圆通,而且说明了其思辨结构的相类。尽管儒家运用“理”、“性”、“命”,释教使用“戒”、“定”、“慧”,道教使用“精”、“气”、“神”等范畴,但都是通过“健顺”、“阴阳”、“体用”等中介环节,而组成儒、释、道的思想逻辑结构的,并论述了儒、释、道三教归一。但陶说仅见皮毛,而未深入剖析。
戴震通过对佛、道宣扬超然实体的剖析,进一步揭示了“理学”的思想渊源。指出了“三教归一”的状况,揭示了庄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或“神识”作为万物的本体,而程、朱“理学”的所谓“理”,便是从佛、道的“真宰”、“真空”转化来的。“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②“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③“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①老、释“以神为天地之本”,程、朱则“以理为气之本”;老、释“以神为气之主宰”,程、朱则“以理为气之主宰”;老、释“以神能生气”,程、朱则“以理能生气”。总之,“彼别形、神为二本”,“此别理、气为二本”。老、庄、佛教割裂“形、神”为“二本”,然后以“神”为“本”;程、朱割裂“理、气”为“二本”,然后以“理”为“本”。戴震通过比较,说明了“理学”和合儒、佛、道的本来面貌。
理学家除吸收道家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和佛教的佛性论和思辨哲学以外,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也为理学家如何地和合儒、释、道指出了方向。宋代的统治集团,显然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统治集团对儒、释、道所采取的兼容并蓄政策,但随着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统治方式的实行,宋统治集团中对于“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情况,十分头痛,迫切需要寻找一种一统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以“一道德”。①于是,宋初的孙复、石介、李觏等从唐末儒学的复兴中得到启发,他们站在儒家的立场,著文反对佛、道。不过,他们主要是从伦理观点上攻击佛、道,没有超出韩愈排佛的基本论点,未能从哲学上加以批判。在当时思想界引起漪澜水波的是欧阳修的《本论》,他倡导以儒家学说为“本”,佛、道为“邪”。认为对佛、道光从社会经济、伦理观点上去批判还不够,照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也不行,应该“修其本以胜之”②,即倡明儒学,以儒学的礼义来代替对佛、道的信仰。同时,旧儒学在唐代却墨守师说,拘泥训诂,限于名物,已显僵化。它在与佛、道的较量中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简单地倡明儒学显然是不行了。因此,一种以儒学为“本”,和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就应运转生了。
这种儒、释、道三教和合的思潮,与统治者的提倡分不开。宋代统治者不仅基本上沿袭了唐的兼容并蓄的政策,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三次到国子监祭祀文宣王,用一品礼,并立十六戟于孔庙门。同时,他倡导佛教,诏诸路寺院:如在显德二年(后周世宗柴荣年号,公元955年)要废未毁的寺院、已毁而仍存的佛像都保留。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行勤和尚等157人到印度求法;五年,文胜和尚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一百六十卷;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诏天下和尚入殿,试经、律、论三学义十余条,全通者,赐紫衣,号为手表僧。宋太宗赵炅既到国子监谒文宣王,又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度僧尼17万人,大建佛寺,大修佛像。七年(公元982年)建译经院,翻译印度佛经,由天息灾、施护,法天负责。是年令赞宁编《宋高僧传》三十卷。另封华山道士陈抟为“希夷先生”。宋真宗赵恒,亲自到曲阜拜祭孔庙,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他敬佛重道,不仅大译佛经,又应西域和尚法贤之请,作《继圣教序》,放在太宗《圣教序》之后,另作《崇释论》,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并诏令撰《景德传灯录》,一年之内度僧尼23万;而且与道士王钦若伪造“天书”,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召见江西上清县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封为“真静先生”。以龙虎山为“受箓院”,立上清宫,免除田租。还诏令:州郡僧、道犯公罪,可以赎罪。官吏无故毁辱僧尼、道士,要受停职处分,老百姓流放千里。宋徽宗赵佶一方面在孔子庙门增立二十四戟,如王者之制,并亲自写匾“大成殿”,颁赐文庙,书写“先圣殿”,为太学辟雍;另一方面,大力提倡道教,任用道士魏汉律等,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王老志为“洞微先生”,直接参与政治。设道官,立《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道士都给官俸,还宣称自己是“上帝元子太霄帝君下降”,要尊奉他为“教主道君皇帝”。由于三教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宋真宗说:“释道二门,有助世教。”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同时,三教的和合,也孕育着理学的转生。
鲁迅先生指出:“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浑;所谓名儒,做几篇伽兰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①“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②理学家沿着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路子,以儒学为骨干和出发点,否定了佛、道宣扬出世、避世,有碍君臣、父子、夫妇等宗法伦理的形式,而吸收佛、道所宣扬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准则;否定了佛、道要在彼岸世界寻求解脱、成佛、成仙,却吸收了佛、道“禁欲”、“主静”以及思辨哲学的宇宙生成的图式,从而建立了理学哲学逻辑结构。于是,待到“三教同源”机运成熟,理学也就形成了。
三、理学的形成
当然,理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经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到南宋的朱熹集其大成。
唐中叶以后,政治上藩镇割据,国势日蹙;思想上释、道、儒三教鼎立,佛盛儒衰。鉴于此情,一些思想家便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国家。出现了黜佛、道而兴儒学的思潮。这个思潮是以古文运动为其先导的。韩愈和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一扫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体,恢复了先秦和两汉质朴的散文文体,而且使古代哲学获得“新生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恢复了孔子的儒学。由文体的改革运动而引起哲学思想的转型,在历史上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韩愈(公元768—824年)继承了从孔孟到董仲舒的“天命论”,他宣扬“天”能决定人的贵贱福祸,“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①如果得罪了“天”,就要降灾祸或刑罚。
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在于提出了一种儒学“道统”说。他认为“道”是一个精神实体,道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遵守和实行“仁”、“义”的原则就是“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②“道统”传授的谱系,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并以自己续“道统”自诩,开理学家所讲“道统”的先河。对此,朱熹赞赏不已。
韩愈在讲“道统”的时候,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突出地抬高孟子的地位。从秦汉以来,儒学并不特别推崇孟子,《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儒学诸子,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第一卷为《序录》,第二至三十卷分别注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不取《孟子》,为当时《孟子》未列入经典之故。韩愈却认为孟子独得孔子之正传,他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③视孟子为诸子之上。二是尊崇《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朱熹认为,汉魏以来,它不被人所重视,韩愈在《原道》中开始强调《大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才逐渐被人所重视。他是这样说的:“《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弟,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①韩愈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应该从“诚意”做起,而达到“治国”、“平天下”。《孟子》、《大学》为理学家所特别崇奉,实自韩愈开其端。韩愈从当时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动摇中,使儒家学说重新抬头,他对儒家学说重新做了诠释和阐发,无疑受到后来理学家的重视。
李翱(公元772—841年)的思想却渗透了佛教的义理。韩愈在讲“性三品”的时候,提到“性”与“情”的关系,然他没有说清楚“善恶”的来源问题。李翱融合佛教的“有情有性”、“无情有性”的佛性论与儒家的心性论,而作《复性书》三篇,发挥孟子的“性善说”。他依据子思的《中庸》②,来说明“恶”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了“性善情恶”说。他说:水本来是清的,泥沙把水弄浑了,泥沙沉淀,水就恢复了清;“性”本是“善”的,喜、怒、哀、惧等“情”把“性”昏蔽了。去掉“情”,就能恢复“善性”③。其实,李翱所讲的“性”,相当于佛教所讲的“本心”,“佛性”;这里所讲的“情”,则相当于佛教的“无明”,“烦恼”。佛教认为,人的本心是“净明圆觉”的,它为“无明”、“烦恼”所昏蔽。因此,去掉“无明”、“烦恼”,便能发明“本心。”
怎样复性呢?李翱认为,先要做到“不虑不思”,然后才能做到“不动心”,即要使“心”处于绝对静止状态,不受丝毫外物的引诱。这种使心进到“寂然不动”的境界,就是《中庸》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时“中”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情欲”就不会发生,也就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他要求通过什么也不想,即禅宗所谓“无念为宗”,来消除心中一切“情欲”杂念,以恢复“善性”,达到精神的绝对超脱,就能与宇宙合一,万物也与我“休作与共”①,通而为一②。
李翱援佛入儒,他的《复性书》简言之,可说是具体而微的理学著作。因此,大得朱熹称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他大谈“性命义理”,“性善情恶”说,把“性”与“情”分别开来。认为“性”是“天”所命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③开启了理学家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先河;第二,他的“弗虑弗思”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即是道学家的所谓“主敬”,是后来理学家争论《中庸》里“未发”、“已发”的先声;第三,他把《中庸》里所讲的“性命之学”,看作是孔孟学说的精髓,因此特别推崇《中庸》。
自秦汉以来,《中庸》也与《大学》一样,并不被人们特别重视,经韩愈和李翱的表彰,后来理学家又纷纷作注解,便取得了与《论语》、《孟子》相当的地位,从而称为《四书》。被看作“六经的阶梯”,都成了儒家的经典。
从提倡儒家“道统”和“性情说”来讲,韩愈和李翱可说是“理学”的先驱。但是,朱熹并不承认。他在编《伊洛渊源录》时,根本不提韩愈和李翱,而把周敦颐捧为理学的开创者,因此,他的学生在《朱子语类》中,把周、程和孔、孟列为一卷,而与《战国汉唐诸子》分开。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异致,然在如何复兴儒学的方法、理路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韩愈以孔子之道为准则,排斥一切,以维护儒家圣贤一脉相传的“道统”。在形式上他似乎捍卫了儒家思想的纯洁性,但他没有根据社会需要的发展而发展儒学,实际上是窒息了儒学。韩愈激烈排斥佛教,主要仍着眼于伦常、费财、夷狄、伤风败俗等老问题,而于佛道思辨哲学几乎未触及。即没有从“本然之全体”上批判佛、道。苏子由评论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①不知形而上的哲学理论问题,这便是韩愈的儒学之所以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症结所在。
柳宗元以孔子之道为准绳,采取有容乃大、吐纳百家的开放方法。他认为儒、佛是可通同、可调和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②这个“合”,是指佛、儒相通之处,这在柳宗元看来,是属于“伸所长”的范围,而佛教的“迹”,是他所黜的“奇袤”。于是,他批评韩愈由于不入佛,而不能区别佛教的“迹”与内容,“外”与“中”之弊。
宋明理学家在总结以往儒释论争的经验教训时,深感韩愈封闭的、简单的方法之弊,而采取了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他们均沿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走出入佛、道的和合途径。
韩、柳都讲“道”,然而韩、柳“道”的内涵和侧重点是不同的。韩愈强调《大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以“正心诚意”来与佛、老相抗衡,而不讲“致知格物”,即不及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被朱熹批评为“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③可谓击中要害。柳宗元与韩愈的分歧便在于此。柳宗元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是“道”。“道”既是自然现象亦是社会现象的概括和抽象。“道”不离“器”,“道”以物为准,依物而存,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道”。“人道”的旨趣在于“利人”、“备事”。而不讲“天”与“神”。所谓“天道”,就是指自然及其规律。如果“道德”是就“人道”而言,则“阴阳”是就“天道”说的。“天道”的具体内容便是“阴阳之气”或称“元气”。
柳宗元的哲学逻辑结构是:
两宋理学家讲道、行道,被认为是重要课题。道学盛于宋,而实萌于韩、柳。然而,韩愈比较偏重伦理道德,而柳宗元合天地自然和社会伦理为一的道学思想体系,对理学家构筑融自然、社会、人类为一的思想体系,影响更深远。
如果说韩愈在建立“道”的学说中,注重《大学》,李翱强调《中庸》,对宋明理学家有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柳宗元重视《周易》,在他的文章中,对《周易》思想顺手拈来,非常贴切而言,对宋明理学家亦有重要影响。理学家讲《易》著《易》,易学逻辑结构几乎是他们思想体系的圭臬。
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韩愈与柳宗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讨论了“天人”关系问题。柳宗元针对韩愈的“天”能赏善罚恶说,明确指出:天地、元气、阴阳如同果蓏、痈痔、草木,都是没有意志,不知报、怒,不会赏、罚的自然物。人事的功、祸与上天无关,是人自己造成的,“非天预乎人也”。这六个字是柳宗元对刘禹锡《天论》三篇的概括。当时刘禹锡鉴于柳宗元《天说》是“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①。把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发展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辨关系。宋明理学家很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并围绕天人关系而扩展为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心与物等问题,使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理学家一方面否定了韩愈天是能赏善罚恶的主宰之天。以“天”为宇宙或自然界,而与柳宗元相通。另一方面,理学家否定了韩愈人为天地之“疣赘”的观点。在韩愈的“天人关系”中,天是主宰,人是天的奴仆,完全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理学家把“人”从“天”的奴役下解脱出来,赋予人以应有的地位,并以人为中心,说明天人关系,而与柳、刘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相接近。
柳宗元在提出天人“不相予”的同时,亦提出了“元气自动”论。他认为,渺茫宇宙的本始,昼夜明暗的交替,天地万物的造始、发展,都是元气的运动变化,天地万物是“元气”的表现形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学说,对后来宋明理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韩愈着重在纲常和道统论方面,那么柳宗元着重在“统合儒释”的思维路径上,以及天人关系、“元气自动”论方面,实开宋明理学学说之先河。柳宗元入佛、道而出佛、道,企图建立一个能融会“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原望,由于宋明理学的转生而完成了。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做知府时,程颢、程颐拜他为师②。他既受佛教影响,曾领教过润州鹤林寺的寿涯,南昌黄龙山的慧南和祖心,庐山归宗寺的了元;又授道入儒,改造道教宇宙生成论,描绘了一个世界生成、发展的《太极图》。从人物的化生到成男成女,都是从这个图式中推演出
动静 变合 妙凝 交感来的。从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演化过程。《太极图》及其《太极图说》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毛奇龄曾说,《太极图说》其中有些说法“直用其(宗密)语”①,是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周敦颐继承李翱,发挥《中庸》里诚的观念,把诚说成是超然的万物本原。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②他还发挥《中庸》中“致中和”作为诚的修养方法。如何达到中?他认为要主静。所谓主静,即是无欲③。“无欲”就达到了“诚立明通”的立人极境界。周敦颐儒学化了的《太极图说》给理学家援佛、道入儒以启示。因此,朱熹称赞周敦颐“闻道甚早”④,“看得这理熟,纵横妙用,只是这数个字,都括尽了。”⑤这大概是朱熹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创者的原因。
邵雍(公元1011—1077年)与周敦颐一样,出入于释、老,而反求诸《六经》。他的《先天图》与周敦颐的《太极图》都来自道教,与邵雍交往甚密的程颢曾说:邵雍之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⑥。《宋史·邵雍传》说:“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显然邵雍问学道教中人李之才,从“本然之全本”上建立其宇宙观。但他并不囿于道教,他的目的是援道入儒,复兴儒学。
他把道教的宇宙生成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吾”融合起来,从心中推衍出宇宙万物。他说:“物有声色气味,人有耳目口鼻。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①物有声、色、气、味,那是人的耳、目、口、鼻等感觉的结果。因而反观内求,什么都具备了。朱熹继承了邵雍的“象数学”及其“一分为二”的思想。邵雍把由“太极”到万物的生成过程,看成是“一分为二”的过程。经朱熹继承和发挥在哲学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张载(公元1020—1077年)继承和发展了柳宗元的思想。
其一,“惟元气存”。即把气作为世界万物多样性的统一基础,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观点。构筑了气本论的哲学逻辑结构。
其二,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从而提出运动变化的泉源是“气”内部的冲突性。“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②的思想。
其三,元气运动变化的形式是相互“交错”。张载将柳宗元的“交错”改造为“交感”。阴阳二端相感,是天地间的普遍现象。
理学的另一奠基者是程颢(公元1032—1085年)和程颐(公元1033—1107年)二程沿着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路子,以儒学为核心,吸收儒家很少讲到而佛、道所津津乐道的宇宙构成、万物化成问题以及其思辨哲学,建立了理本论哲学逻辑结构。正如程颢所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二程把他们体贴出来的“天理”(“理”)作为世界万物的终极根据,可说是受佛教三论宗、华严宗的启发。尽管先秦以来《孟子》、《周易·系辞传》都讲到“理”,但没有作为其哲学的形上学范畴,惟独二程把“理”提升为宇宙的根据。在二程的心目中,“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又是社会的最高原则,并体现为“三纲五常”。①北宋社会要求哲学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作出系统地回答。二程适应了这种需要,他们融合三教,把自然观、体认论、价值观、人性论、道德论、工夫论等各方面问题统统纳入理学体系,提出了“理气”、“道器”、“形而上形而下”、“格物致知”、“天理人欲”、“道心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等一系列理学家所讨论不休的问题,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因而,二程深得朱熹推崇。朱熹认为,孔子死后,得“圣人”之心传的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直到二程出来,“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②,所谓圣人的心传祕旨才又续了下来。所以,他说:“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③把个二程与孔、孟并提。有时,朱熹甚至把程颢比为颜渊,程颐比之孟子,“明道可比颜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处,然伊川收束检制处,孟子却不能到。”④这就是说,孟子与程颐各有千秋,譬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⑤把二程抬到很高的地位。
宋明理学由于二程建立了理本论的哲学逻辑结构和张载建立了气本论的哲学逻辑结构,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朱熹吸收二程的“理”作为其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又改造张载的气作为“理”返回到“物”的中介,起着沟通理与物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而建立了哲学逻辑结构。
总之,理学的转生和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是北宋初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冲突的化解;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而和合结晶;是重建道德形上学的需要;是社会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智慧。
附注
①《孟子·告子》,《习学纪言序目》卷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6页。
②《孟子·公孙丑》,《习学纪言序目》卷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9页。叶适论“义理”甚多,如:“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题姚令威西溪集》,《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14页。
③《答范巽之书》,《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9页。
①《上孙叔曼侍郎求写兄墓志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3页。
②《程氏遗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以下简称《文集》。
③《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69页。
④同上。
⑤《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①《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水心文集》卷二,《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页。
②《经说》,《困学纪闻》卷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74页。
①转引自《经说》,《困学纪闻》卷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74页。
①苏轼主张:“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中,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东坡后集》卷十六)
②《伊川年谱》,《伊洛渊源录》卷四。
①参见《伊洛渊源录》卷三。
②《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
①《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②《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③参见《朱子语类》卷十八
④同上。
⑤《朱子语类》卷九。
⑥《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⑦《思辨录》卷二。
⑧《朱子语类》卷十一。
①《朱子语类》卷六十。
②《语录中》《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
③《明道先生行状》,《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8页。
④《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①参见拙作:《论汉魏-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和合流》,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260页。
①《宋史·朱震传》:震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其《经筵表》有云:“陈抟以《太极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黄宗羲在《太极图辩》中说:“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尧夫。修以《无极图》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寿涯。”(《濂溪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十二)可见邵雍和周敦颐的《先天图》和《太极图》来自道家。
②王弼:《周易略例·明彖》,《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1页。
①王弼:《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2页。
②《华严法界观门注》。
①杜顺:《华严法界观门》。
①《南村辍耕录》卷三十。
②《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③同上书,第19页。
①《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8页。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四。
②《本论下》,《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①《准风月谈·吃教》。
②《华盖集·补白》。按:当时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风气很盛,智园在《闲居编·自序》中说:“释智园,字无外,自号中庸子。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杨、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
①《与卫中行书》,《韩昌黎集》卷十七。
②《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
③《送王秀才序》,《韩昌黎集》卷二〇。
①《大学或问上》,《四书或问》,《朱熹全书》(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②北宋欧阳修说:“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耳。”(《读李翱文》,《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三)
③见《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三。
①《复性书·下》,《李文公集》卷三。
②“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复性书·下》,《李文公集》卷三。
③《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三。
①《原道注》,《韩昌黎集》卷十一。
②《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页。
③《大学或问·上》,《四书或问》,《朱熹全书》(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①《天论上》、《柳宗元集》卷十六附,第444页。
②《伊洛渊源录》卷一,《濂溪先生事状》记载:“洛人程公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学焉。”
①《西河合集·太极图说遗议》引胡汲仲《大同论》。宗密(公元780—840年)号圭峰,华严宗第五祖,荷泽神会的四传弟子。武内义雄博士说:“宗密《原人论》的一节,被周茂叔的《太极图说》所采用。”(《支那思想史》第247页)。
②《通书·诚上》,《周子全书》卷七。
③《太极图说·自注》,《周子全书》卷二。
④《濂溪先生事状》《伊洛渊源录》卷一。
⑤《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⑥《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二程全书·文集》卷三。
①《乐物吟》,《击壤集》卷十九。
②《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200页。
③《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
①参见《二程全书·遗书》卷五、十九。
②《经筵讲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③《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④同上。
⑤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