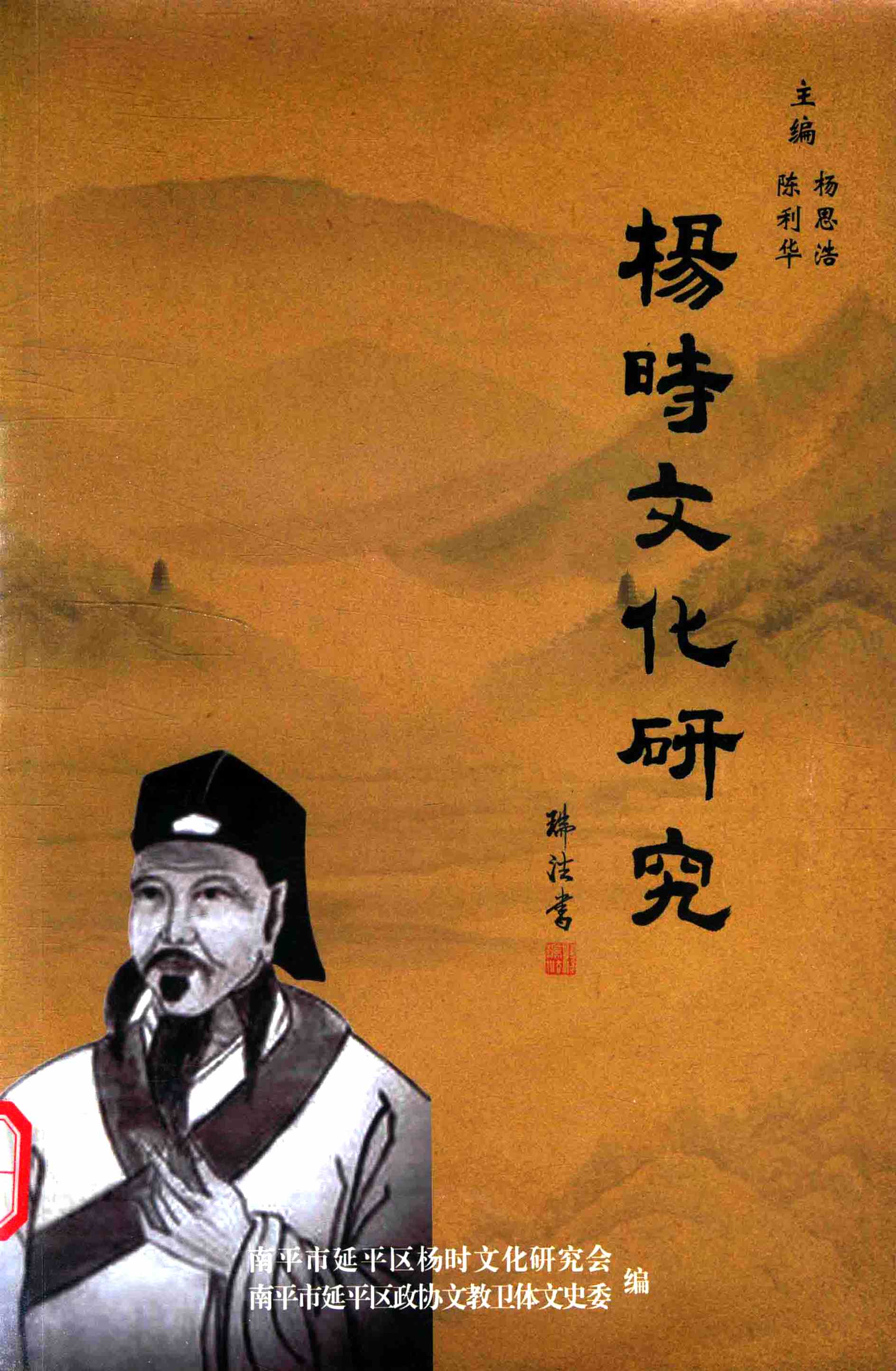内容
科举制是隋唐时期中国的选官制度,“学而优则仕”是士人学子追求的目标,而科举又以章词取士,流于章句,导致学校教育重艺不重德,偏离了原始儒家仁政德政的思想。为了适应宋代政治革新的需要,理学家们从经世致用出发,在“理一分殊”本体论的思想框架之下,梳理出古今相通的理路,建构体用结合的文化形式,以期培养“明体达用”双重人格的人才。杨时就是在此新旧儒学转换的建构中,沿着“明体达用”的路径,求学问道,传播二程理学,使东南地域的书院呈现出有体有用的人格文化新模式。“程氏正宗”不仅阐明杨时之学直承二程理学,而且是对杨时书院人格化教育的高度评价。
一、求学问道,得“明体达用”之传“明体达用之学”之“体”是指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是指将道德标准付诸实践,因此也称“体用之学”。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他提出的宇宙生成论、万物生化论、圣人主静人性论具有理学开山浚源之功。孙复、石介、胡瑗“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也是构建“体用之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中胡瑗业绩最著,因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其教学方法得到朝廷肯定。清人全祖望称“安定(胡瑗)笃实”,庆历间“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二程继承周敦颐和“宋初三先生”的理学思想,提出“理一分殊”的天理论,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将其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他们认为,“天者,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下)“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同上,卷十五)程颢说:“《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同上,卷十四)程颐则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三)就像佛教说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玄觉《永嘉证道歌》)而理学家说的理或理一也称“道”或“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或准则。“天有是事,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程颐还把“理一”比喻为“公”,把“分殊”比喻为“私”,“公”为体为本,“私”为行为用,是“公”在事事物物的显现。“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同上,卷十五)可见,二程既讲“理一”之体,又强调“分殊”之用,而“分殊”必归于“理一”,正如二程比喻“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同上)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仁则一,不仁则二”。(《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上)二程要求学者要在随事的“分殊”之“用”中,精察力行“理一”。
应该说,原始儒家在践履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们进修德业提供了完满的路径,甚至对人君德礼仁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缺憾在于没有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地位。二程的理本论把伦理纲常推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的不易之理,并且提出通过“格物致知”,在“分殊”中体认“天理”、践履“天理”的思路,建构了体用结合、有体有用的理学思想体系,以天理的高度张扬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品格,成为后代书院的精神追求。因此,黄宗羲的老师刘蕺山说:“程子首识仁,不是教人悬空参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上)二程“理一分殊”为杨时书院人格化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杨时勤奋好学,宋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次年授汀州司户参军未赴,杜门潜心研究经史,入仕后一边治事,一边问道求学。元丰四年(1081),他北上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为门下有此高足感到高兴,称“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成为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的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离开时,程颢默语:“吾道南矣。”杨时成为理学南渡之鼻祖。元丰八年(1085)程颢逝世。元祐八年(1093),杨时41岁。这年他又与游酢一同北上向伊川(程颐)求学,发生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程门立雪”佳话。其后,杨时通过书信向程颐请益。
杨时得二程“理一分殊”之传源于张载的《西铭》。《西铭》是一篇论述宇宙人生的精典文章,杨时的老师程颢说“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同上,卷十八《横渠学案》下)又说“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同上)程颐对《西铭》所言也深信不疑。但杨时却提出质疑,认为《西铭》中阐发“民吾同胞,物吾物也”的观点,与墨子爱无差等的“兼爱”说相类。于是,绍圣三年(1096)写《论西铭》向程颐请教,与之“辩论往复”。杨时在信中质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爱”。(同上)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指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并非墨氏兼爱之说,杨时得二程真传。
《宋史·杨时传》说:“(杨时)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杨时是理学南渡的鼻祖,自然也是第一位将“理一分殊”南传的学生。
二、创建书院,传播“体用之学”宋庆历年间,“宋初三先生”传授儒家经典和教学之法受到朝廷肯定,但到了崇宁二年(1103),受朝中大臣范致虚谗言,二程理学被视为异端邪说。一时间,士大夫与学者谈“理”变色,无一人复敢言道。杨时南归后,承担起传播理学的使命,他创建书院、著书立说,“浸淫经书,推广师说”(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广播二程体用之学,为书院塑造人格化教育孜孜不倦。
杨时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利用学官与学者集于一身之便创建书院,开展讲学活动。在萧山讲学,“四方之士闻时名,不远千里来从游”。(民国十四年《萧山县志》卷十二)在东林书院,弟子千余人从游,培养出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一批学术颇有造诣的门人弟子。
传统儒学主要体现的是建立个人践履基础上的修身精神,而“理一分殊”则强调有体有用,体用结合,而且要“明理达用”。作为“洛学南渡之家”、“程氏正宗”的杨时,在塑造书院人格化教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事天循理,格物致知。杨时对二程“理一分殊”体用之学有独到的见解,虽然程颐在回答他《西铭》中有关“理一分殊”问题并没有详细展开,但杨时贯通体用之旨,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结合,不可分离,体普遍流行,用是体的显现。
杨时说:“《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谓事天者,循理而已。”(《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案》下)“事”在这里是动词,广义的“事”指人类的一切活动,狭义的“事”有“治理”“处置”之意;“天”是指宇宙天地,具体说就是万事万物。而这个“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理”有正与不正之分,主体行为与客体必须中节适度是正理,也就是“理一”。反之,是不正之理,即本来天下只一个理变成了与正理相悖的理外之理。二程说:“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二程遗书》卷十七)又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朱熹、吕祖谦编,查洪德注译《近思录》卷一《道体》,第3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只注书名)中节适度才是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杨时用体用关系对应“理一分殊”,用穿鞋戴帽比喻“理一分殊”“中节”之善:“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杨时集》卷十一《京师所闻》)就是说,“分殊”所展现的景象必须与体适中,就像人不能把鞋“戴”在头上,也不能把帽子“穿”在脚上,否则就不中节,不合“理一”之体。
杨时常常通过书信与诸生论学。他把善作为明天理的标准,把穷理视为致知的手段,把诚视为立志的条件。他在《答李杭》的信中说:“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达矣!”(《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知道什么是善,还要知道所以为善的道理,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格物致知。因为大千世界物的数量千千万,而物之理难以穷尽。
杨时认为格物致知要诚实无欺,真实无妄,才能明白事理。如果不立诚,即使知道“理”之所在也不能践行。他在《答学者》中说:“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所谓止者,乃其至处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同上)事天循理要身体心验、闲静默识,否则只是诵章词数学之类的知识。他在《寄翁好德》信中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同上)他强调致知循理还要力行。他在《答吕秀才》信中用问道走路作比喻:“自致知至于虑而后得,进德之序也。譬之适四方者,未知所之,必问道所从出,所谓致知也。知其所之,则知止矣,语至则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学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同上)问得路径的方向也是致知,但只是语到而行未到,只有语到行到才算知至,这就是力行的重要性。
总之,杨时在肯定事天循理的同时,又认为教育的作用只是教人知之,学者还必须践履力行,才是至善之理。
2、仁为大本,用中体仁。天地之间一理而已,在天为规律,在人则为准则,而仁是人事的本体,是有序和谐的表征。程氏说:“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程氏经说·论语解》)在理学家看来,体即仁,仁即体。张载说“无一物之不体也”、“无一物而非仁也”。(张载《正蒙·天道》)而仁散于事事物物之中,须用身体心验,明道引用《论语·子张》所说:“‘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第90页)二程说:“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同上,第85页)这个体就是仁,即伦理纲常,“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同上,第84页)就是强调伦理纲常具有立于天地的最高地位,人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公”(本或体)有丝毫差别,否则就不是人君应有的品格。
杨时继承张载和二程用中体仁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杨时用“理一分殊”阐明仁与义的关系,他在《答胡康侯》信中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在这里,他把仁视为“理一”,是体是本;把义看成是“分殊”,为行为用,二者不同,但又相互联系。仁作为“理一”本体,普遍流行,义作为“分殊”之用,要展现仁的光辉,二者无“铢分之差”才算精妙。杨时对“理一分殊”的理解可谓精到。杨时还认为人要明理义,才能内心与外在合二为一,才能安身立命。他说:“夫精义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同上)杨时认为仁是王道的根柢,要怀敌附远,实现天下大治,就要得人才,要得人才就要得人心,要得人心人君要怀仁人之心。因此,他强调一方面人君要有仁人之心,另一方面事君的臣子也应担当起使人君有仁人之心的责任,王道就能通于天下。“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则王道行矣”。(同上)杨时强调经义的重要性,认为经义是可以践履并流行于寻常事物之中的。他说“经义至不可践履处,便非经义。若圣人之言,岂有人做不得处。学者所以不免求之释、老,为其有高明处。如《六经》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认了。曾不知圣人将妙理只于寻常事说了。”(同上)就是说寻常事中有本体,圣人的妙理都说在生活日用之中了。杨时对科举制培养出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格提出强烈抨击,认为入仕之人只图在功利上。他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同上)因此,他要求学生不能停留在笔墨和口舌上,而要精思之,力行之。
事实上,尽管理学家初步搭起了“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框架,并强调要在“分殊”中体认天理,但当时的社会上仍然存在体用分隔的现象,表现在官场上就是虚夸。杨时揭露官场的时弊说:“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风俗,怎抵当他!”(同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遵循体用一致、知行合一的准则。他说:“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记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同上)杨时提出要克服万样私意,所为与本相同,无异为朝廷治国培养人才开出一道良方。
3、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杨时承认儒家博爱,但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说法,而肯定二程所说的“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近思录》卷一《道体》,第46页)的观点,也就是承认儒家所说的爱有“差等”。他说:“河南先生言‘理一分殊’。……所谓分殊,即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分不能无等差。”(《杨时集》卷十一《京师所闻》)他认为博爱之施,应“亲疏远近各当其分”。(同上,卷十六《书一》)虽然杨时的差等论是论证封建社会亲疏尊卑的合理性,但从“理一”的角度看,既符合自然界生生之理,也符合儒家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
儒家提倡“为已之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儒家预想的大同社会,是从个体向全体,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全面展开。《大学》开篇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修身进德的路径就体现出爱有差等的思想。个人是家庭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致知然后诚意,诚意然后正心,正心然后修身,修身然后齐家,齐家然后治国,治国然后平天下。爱从自身开始,向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递进,不断扩大,而这种递进扩大就有差等亲疏之分。如果爱无差等亲疏,亲亲变成亲民,爱物变成亲物,岂非乱了人伦和秩序。因此,儒家强调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修养,通过个人修身养性,付之实行,推己及人。从爱己爱家推向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从法制的角度看,爱有差等也符合法理精神,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是遗产的继承。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的两个顺序为,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依据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血缘关系和亲疏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决定的,用理学家的话说就是爱的差等决定的,说明爱有差等符合法制原则。而儒家与法律规定的爱有差等相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它能扩大到法律难以启及的社会各个层面。
4、宽予抑取,构建和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儒家推崇的范式。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杨时作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不妄取”比“不妄予”更具实用性。
杨时说:“有能捐一金而不顾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顾者,未必能捐百金。”如果能伸明义理,“虽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就是说,予是出于自愿,非强力所为,有人奉献自然好,无人奉献亦无妨,因为可以通过国家有计划的救济办法解决困难,关键是要把住“妄取”的关。因为“妄取”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贫富不均,由此引发社会混乱。
“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是儒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名言。但是,“不均”的现象自古有之,问题是引起“不均”的原因,有自然地理地、灾害、勤惰等引起的不均,有以权敛财、以公肥私造成的不均。前者是自然现象,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或教育人民务农重谷增加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后者则无法用发展生产解决,少数人不正当聚敛财富,造成社会不均,从而造成社会不安。儒家一方面提倡“足食之本在农”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极力反对敛财行为。杨时的“不妄取”比传统儒学取之有道更具现实意义。
虽然囿于篇幅,不能详尽例举杨时“体用之学”之大观。但杨时传承二程理学,并从体用的角度阐发传播“理一分殊”哲学思想,为书院塑造人格化人才作出贡献,得到学者的高度称赞。杨时的师友、给事中朱震上疏言,先生(杨时)尝“排邪说以正天下学术之谬”。(《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全祖望引慈溪黄氏说:“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同上)肯定杨时为传播体用之学所做的贡献。
三、身体力行,践履“体用之学”在“南剑三先生”、“延平四贤”中,杨时为官时间最长,任职的地方最广,因而他的“体用之学”的人格化塑造多体现在他的治事上。
二程认为,学者须事事体认天理。有人问二程:“时中如何?”二程回答:“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中非中,而堂为中;言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二程遗书》卷十八)就是说,“分殊”之用要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各自的角色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事方法,确定符合天理的最佳效果。就一厅而言以中央为中,一家而言以堂为中,一国而言以国家为中。“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湖州讲学设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要求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就是说,虽事事有天理,但表现各不同,必须各尽天份,如为官者以使民安居乐业为己任,讲武者以抵御寇患为己任,水利者以筑坝利田为己任,历算者以精通运算为已任。
杨时身为一方地方官,担负着综合“治事”的职责,因为心中有“民者邦之本,一失其心则本摇也”的情怀,他的人格化塑造多从有体有用的实践中体现。每到一地他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伸明义理,做有体有用的表率,使义理不流虚谈之失。
元符元年(1098),他在虔州任司法时,秉持生民之“理”,秉公办案,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说:“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元祐八年(1093),在浏阳任知县时,翌年夏末秋初,当地发生严重旱灾,灾民背井离乡,他秉持恤民之理,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如实向上反映灾情,争取赈灾粮款;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当地成了“水泽之国”,他写《与州牧书》,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崇宁五年(1106),他到余杭任知县,“简易不为烦苛,远近悦服”(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树立廉政形象。
在余杭期间,他不畏权贵,抵制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勔、李邦彦等假借“便民”实为圈地的图谋。同时,针对蔡京、童贯、朱勔等人为迎合宋徽宗赵佶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花异石建龙德宫,在《余杭见闻》一文中揭露他们知法犯法、暴政虐民的罪行:“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要求朝廷铲除祸根。政和二年(1112),在萧山任知县时,率百姓筑湖,蓄水灌田。所筑之湖称“湘湖”,周围80余里,灌溉农田3702余亩。(林家齐《杨时纪略》,《朱熹与闽学渊源》,第65页,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经过治理,湘湖成为种养两利的肥沃之区,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当地百姓感其德,为之立庙,画其像以祭。
杨时晚年立朝,金人南侵,宋室处于危亡之秋。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提出多项战策。如针对朝廷“虚内事外”的用兵策略,提出“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宋史·杨时传》)又说朝廷应激励士兵奋勇御敌,他说:“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燃,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同上)他要求朝廷要收拾人心,“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以恃”。
(同上)由此可见,杨时不论是讲学还是为官治事,都像儒家提倡的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使社会最大限度地趋于和谐,表现出理学家人文主义的品格和魅力。因此,其足之所履,“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同上)由于杨时善政,其名声在宋代就传到高丽。宣和五年(1123),朝廷使臣路允迪、付墨卿出使高丽(朝鲜)。高丽王问二使者“龟山安在?”(同上)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
而升堂覩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朱子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杨时的体用之学对朱熹理学影响至深,对闽北书院人格化塑造也影响至深。闽北的书院早在唐末就已出现,但那时的书院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教育家族子弟的私塾。北宋时期,又有建阳学者江侧筑室石壁山,建阳宋咸的霄峰精舍,浦城章得象、杨徽之、杨亿分别所筑的读书堂,崇安江贽的叔圭精舍及朱松在政和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吸引了众多弟子读学讲学,但这些书堂书院的目的多是为了应试科举而设,以理学思想为宗旨、塑造体用结合人才的书院尚未形成。杨时南传理学,并在武夷山、建阳、将乐等地创建书院,授徒讲学,闽北的书院才真正转变为塑造人格化教育的场所。经过120年数代理学家承前启后传承,到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书院作为培养体用结合人才的教育模式自宋至清沿袭了七、八百年。由此可见,杨时对塑造书院人格化教育功不可没。
(作者系南平市台办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朱子文化》编辑部主任)
一、求学问道,得“明体达用”之传“明体达用之学”之“体”是指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是指将道德标准付诸实践,因此也称“体用之学”。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他提出的宇宙生成论、万物生化论、圣人主静人性论具有理学开山浚源之功。孙复、石介、胡瑗“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也是构建“体用之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中胡瑗业绩最著,因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其教学方法得到朝廷肯定。清人全祖望称“安定(胡瑗)笃实”,庆历间“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二程继承周敦颐和“宋初三先生”的理学思想,提出“理一分殊”的天理论,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将其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他们认为,“天者,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下)“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同上,卷十五)程颢说:“《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同上,卷十四)程颐则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三)就像佛教说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玄觉《永嘉证道歌》)而理学家说的理或理一也称“道”或“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或准则。“天有是事,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下)程颐还把“理一”比喻为“公”,把“分殊”比喻为“私”,“公”为体为本,“私”为行为用,是“公”在事事物物的显现。“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同上,卷十五)可见,二程既讲“理一”之体,又强调“分殊”之用,而“分殊”必归于“理一”,正如二程比喻“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同上)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仁则一,不仁则二”。(《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上)二程要求学者要在随事的“分殊”之“用”中,精察力行“理一”。
应该说,原始儒家在践履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们进修德业提供了完满的路径,甚至对人君德礼仁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缺憾在于没有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地位。二程的理本论把伦理纲常推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的不易之理,并且提出通过“格物致知”,在“分殊”中体认“天理”、践履“天理”的思路,建构了体用结合、有体有用的理学思想体系,以天理的高度张扬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品格,成为后代书院的精神追求。因此,黄宗羲的老师刘蕺山说:“程子首识仁,不是教人悬空参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上)二程“理一分殊”为杨时书院人格化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杨时勤奋好学,宋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次年授汀州司户参军未赴,杜门潜心研究经史,入仕后一边治事,一边问道求学。元丰四年(1081),他北上颍昌拜程颢为师。程颢为门下有此高足感到高兴,称“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成为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的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离开时,程颢默语:“吾道南矣。”杨时成为理学南渡之鼻祖。元丰八年(1085)程颢逝世。元祐八年(1093),杨时41岁。这年他又与游酢一同北上向伊川(程颐)求学,发生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程门立雪”佳话。其后,杨时通过书信向程颐请益。
杨时得二程“理一分殊”之传源于张载的《西铭》。《西铭》是一篇论述宇宙人生的精典文章,杨时的老师程颢说“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同上,卷十八《横渠学案》下)又说“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同上)程颐对《西铭》所言也深信不疑。但杨时却提出质疑,认为《西铭》中阐发“民吾同胞,物吾物也”的观点,与墨子爱无差等的“兼爱”说相类。于是,绍圣三年(1096)写《论西铭》向程颐请教,与之“辩论往复”。杨时在信中质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爱”。(同上)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指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并非墨氏兼爱之说,杨时得二程真传。
《宋史·杨时传》说:“(杨时)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杨时是理学南渡的鼻祖,自然也是第一位将“理一分殊”南传的学生。
二、创建书院,传播“体用之学”宋庆历年间,“宋初三先生”传授儒家经典和教学之法受到朝廷肯定,但到了崇宁二年(1103),受朝中大臣范致虚谗言,二程理学被视为异端邪说。一时间,士大夫与学者谈“理”变色,无一人复敢言道。杨时南归后,承担起传播理学的使命,他创建书院、著书立说,“浸淫经书,推广师说”(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广播二程体用之学,为书院塑造人格化教育孜孜不倦。
杨时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利用学官与学者集于一身之便创建书院,开展讲学活动。在萧山讲学,“四方之士闻时名,不远千里来从游”。(民国十四年《萧山县志》卷十二)在东林书院,弟子千余人从游,培养出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一批学术颇有造诣的门人弟子。
传统儒学主要体现的是建立个人践履基础上的修身精神,而“理一分殊”则强调有体有用,体用结合,而且要“明理达用”。作为“洛学南渡之家”、“程氏正宗”的杨时,在塑造书院人格化教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事天循理,格物致知。杨时对二程“理一分殊”体用之学有独到的见解,虽然程颐在回答他《西铭》中有关“理一分殊”问题并没有详细展开,但杨时贯通体用之旨,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结合,不可分离,体普遍流行,用是体的显现。
杨时说:“《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谓事天者,循理而已。”(《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案》下)“事”在这里是动词,广义的“事”指人类的一切活动,狭义的“事”有“治理”“处置”之意;“天”是指宇宙天地,具体说就是万事万物。而这个“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理”有正与不正之分,主体行为与客体必须中节适度是正理,也就是“理一”。反之,是不正之理,即本来天下只一个理变成了与正理相悖的理外之理。二程说:“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二程遗书》卷十七)又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朱熹、吕祖谦编,查洪德注译《近思录》卷一《道体》,第3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只注书名)中节适度才是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杨时用体用关系对应“理一分殊”,用穿鞋戴帽比喻“理一分殊”“中节”之善:“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杨时集》卷十一《京师所闻》)就是说,“分殊”所展现的景象必须与体适中,就像人不能把鞋“戴”在头上,也不能把帽子“穿”在脚上,否则就不中节,不合“理一”之体。
杨时常常通过书信与诸生论学。他把善作为明天理的标准,把穷理视为致知的手段,把诚视为立志的条件。他在《答李杭》的信中说:“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达矣!”(《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知道什么是善,还要知道所以为善的道理,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格物致知。因为大千世界物的数量千千万,而物之理难以穷尽。
杨时认为格物致知要诚实无欺,真实无妄,才能明白事理。如果不立诚,即使知道“理”之所在也不能践行。他在《答学者》中说:“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所谓止者,乃其至处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同上)事天循理要身体心验、闲静默识,否则只是诵章词数学之类的知识。他在《寄翁好德》信中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同上)他强调致知循理还要力行。他在《答吕秀才》信中用问道走路作比喻:“自致知至于虑而后得,进德之序也。譬之适四方者,未知所之,必问道所从出,所谓致知也。知其所之,则知止矣,语至则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学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同上)问得路径的方向也是致知,但只是语到而行未到,只有语到行到才算知至,这就是力行的重要性。
总之,杨时在肯定事天循理的同时,又认为教育的作用只是教人知之,学者还必须践履力行,才是至善之理。
2、仁为大本,用中体仁。天地之间一理而已,在天为规律,在人则为准则,而仁是人事的本体,是有序和谐的表征。程氏说:“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程氏经说·论语解》)在理学家看来,体即仁,仁即体。张载说“无一物之不体也”、“无一物而非仁也”。(张载《正蒙·天道》)而仁散于事事物物之中,须用身体心验,明道引用《论语·子张》所说:“‘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第90页)二程说:“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同上,第85页)这个体就是仁,即伦理纲常,“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同上,第84页)就是强调伦理纲常具有立于天地的最高地位,人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公”(本或体)有丝毫差别,否则就不是人君应有的品格。
杨时继承张载和二程用中体仁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杨时用“理一分殊”阐明仁与义的关系,他在《答胡康侯》信中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在这里,他把仁视为“理一”,是体是本;把义看成是“分殊”,为行为用,二者不同,但又相互联系。仁作为“理一”本体,普遍流行,义作为“分殊”之用,要展现仁的光辉,二者无“铢分之差”才算精妙。杨时对“理一分殊”的理解可谓精到。杨时还认为人要明理义,才能内心与外在合二为一,才能安身立命。他说:“夫精义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同上)杨时认为仁是王道的根柢,要怀敌附远,实现天下大治,就要得人才,要得人才就要得人心,要得人心人君要怀仁人之心。因此,他强调一方面人君要有仁人之心,另一方面事君的臣子也应担当起使人君有仁人之心的责任,王道就能通于天下。“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则王道行矣”。(同上)杨时强调经义的重要性,认为经义是可以践履并流行于寻常事物之中的。他说“经义至不可践履处,便非经义。若圣人之言,岂有人做不得处。学者所以不免求之释、老,为其有高明处。如《六经》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认了。曾不知圣人将妙理只于寻常事说了。”(同上)就是说寻常事中有本体,圣人的妙理都说在生活日用之中了。杨时对科举制培养出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格提出强烈抨击,认为入仕之人只图在功利上。他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同上)因此,他要求学生不能停留在笔墨和口舌上,而要精思之,力行之。
事实上,尽管理学家初步搭起了“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框架,并强调要在“分殊”中体认天理,但当时的社会上仍然存在体用分隔的现象,表现在官场上就是虚夸。杨时揭露官场的时弊说:“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风俗,怎抵当他!”(同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遵循体用一致、知行合一的准则。他说:“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记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同上)杨时提出要克服万样私意,所为与本相同,无异为朝廷治国培养人才开出一道良方。
3、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杨时承认儒家博爱,但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说法,而肯定二程所说的“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近思录》卷一《道体》,第46页)的观点,也就是承认儒家所说的爱有“差等”。他说:“河南先生言‘理一分殊’。……所谓分殊,即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分不能无等差。”(《杨时集》卷十一《京师所闻》)他认为博爱之施,应“亲疏远近各当其分”。(同上,卷十六《书一》)虽然杨时的差等论是论证封建社会亲疏尊卑的合理性,但从“理一”的角度看,既符合自然界生生之理,也符合儒家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
儒家提倡“为已之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儒家预想的大同社会,是从个体向全体,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全面展开。《大学》开篇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修身进德的路径就体现出爱有差等的思想。个人是家庭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致知然后诚意,诚意然后正心,正心然后修身,修身然后齐家,齐家然后治国,治国然后平天下。爱从自身开始,向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递进,不断扩大,而这种递进扩大就有差等亲疏之分。如果爱无差等亲疏,亲亲变成亲民,爱物变成亲物,岂非乱了人伦和秩序。因此,儒家强调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修养,通过个人修身养性,付之实行,推己及人。从爱己爱家推向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从法制的角度看,爱有差等也符合法理精神,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是遗产的继承。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的两个顺序为,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依据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血缘关系和亲疏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决定的,用理学家的话说就是爱的差等决定的,说明爱有差等符合法制原则。而儒家与法律规定的爱有差等相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它能扩大到法律难以启及的社会各个层面。
4、宽予抑取,构建和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儒家推崇的范式。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杨时作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不妄取”比“不妄予”更具实用性。
杨时说:“有能捐一金而不顾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顾者,未必能捐百金。”如果能伸明义理,“虽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就是说,予是出于自愿,非强力所为,有人奉献自然好,无人奉献亦无妨,因为可以通过国家有计划的救济办法解决困难,关键是要把住“妄取”的关。因为“妄取”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贫富不均,由此引发社会混乱。
“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是儒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名言。但是,“不均”的现象自古有之,问题是引起“不均”的原因,有自然地理地、灾害、勤惰等引起的不均,有以权敛财、以公肥私造成的不均。前者是自然现象,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或教育人民务农重谷增加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后者则无法用发展生产解决,少数人不正当聚敛财富,造成社会不均,从而造成社会不安。儒家一方面提倡“足食之本在农”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极力反对敛财行为。杨时的“不妄取”比传统儒学取之有道更具现实意义。
虽然囿于篇幅,不能详尽例举杨时“体用之学”之大观。但杨时传承二程理学,并从体用的角度阐发传播“理一分殊”哲学思想,为书院塑造人格化人才作出贡献,得到学者的高度称赞。杨时的师友、给事中朱震上疏言,先生(杨时)尝“排邪说以正天下学术之谬”。(《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全祖望引慈溪黄氏说:“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同上)肯定杨时为传播体用之学所做的贡献。
三、身体力行,践履“体用之学”在“南剑三先生”、“延平四贤”中,杨时为官时间最长,任职的地方最广,因而他的“体用之学”的人格化塑造多体现在他的治事上。
二程认为,学者须事事体认天理。有人问二程:“时中如何?”二程回答:“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中非中,而堂为中;言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二程遗书》卷十八)就是说,“分殊”之用要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各自的角色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事方法,确定符合天理的最佳效果。就一厅而言以中央为中,一家而言以堂为中,一国而言以国家为中。“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湖州讲学设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要求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就是说,虽事事有天理,但表现各不同,必须各尽天份,如为官者以使民安居乐业为己任,讲武者以抵御寇患为己任,水利者以筑坝利田为己任,历算者以精通运算为已任。
杨时身为一方地方官,担负着综合“治事”的职责,因为心中有“民者邦之本,一失其心则本摇也”的情怀,他的人格化塑造多从有体有用的实践中体现。每到一地他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伸明义理,做有体有用的表率,使义理不流虚谈之失。
元符元年(1098),他在虔州任司法时,秉持生民之“理”,秉公办案,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说:“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元祐八年(1093),在浏阳任知县时,翌年夏末秋初,当地发生严重旱灾,灾民背井离乡,他秉持恤民之理,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如实向上反映灾情,争取赈灾粮款;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当地成了“水泽之国”,他写《与州牧书》,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崇宁五年(1106),他到余杭任知县,“简易不为烦苛,远近悦服”(同上,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树立廉政形象。
在余杭期间,他不畏权贵,抵制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勔、李邦彦等假借“便民”实为圈地的图谋。同时,针对蔡京、童贯、朱勔等人为迎合宋徽宗赵佶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花异石建龙德宫,在《余杭见闻》一文中揭露他们知法犯法、暴政虐民的罪行:“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要求朝廷铲除祸根。政和二年(1112),在萧山任知县时,率百姓筑湖,蓄水灌田。所筑之湖称“湘湖”,周围80余里,灌溉农田3702余亩。(林家齐《杨时纪略》,《朱熹与闽学渊源》,第65页,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经过治理,湘湖成为种养两利的肥沃之区,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当地百姓感其德,为之立庙,画其像以祭。
杨时晚年立朝,金人南侵,宋室处于危亡之秋。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提出多项战策。如针对朝廷“虚内事外”的用兵策略,提出“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宋史·杨时传》)又说朝廷应激励士兵奋勇御敌,他说:“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燃,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同上)他要求朝廷要收拾人心,“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以恃”。
(同上)由此可见,杨时不论是讲学还是为官治事,都像儒家提倡的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使社会最大限度地趋于和谐,表现出理学家人文主义的品格和魅力。因此,其足之所履,“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同上)由于杨时善政,其名声在宋代就传到高丽。宣和五年(1123),朝廷使臣路允迪、付墨卿出使高丽(朝鲜)。高丽王问二使者“龟山安在?”(同上)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
而升堂覩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朱子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杨时的体用之学对朱熹理学影响至深,对闽北书院人格化塑造也影响至深。闽北的书院早在唐末就已出现,但那时的书院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教育家族子弟的私塾。北宋时期,又有建阳学者江侧筑室石壁山,建阳宋咸的霄峰精舍,浦城章得象、杨徽之、杨亿分别所筑的读书堂,崇安江贽的叔圭精舍及朱松在政和创建的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吸引了众多弟子读学讲学,但这些书堂书院的目的多是为了应试科举而设,以理学思想为宗旨、塑造体用结合人才的书院尚未形成。杨时南传理学,并在武夷山、建阳、将乐等地创建书院,授徒讲学,闽北的书院才真正转变为塑造人格化教育的场所。经过120年数代理学家承前启后传承,到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书院作为培养体用结合人才的教育模式自宋至清沿袭了七、八百年。由此可见,杨时对塑造书院人格化教育功不可没。
(作者系南平市台办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朱子文化》编辑部主任)
相关人物
罗小平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杨时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