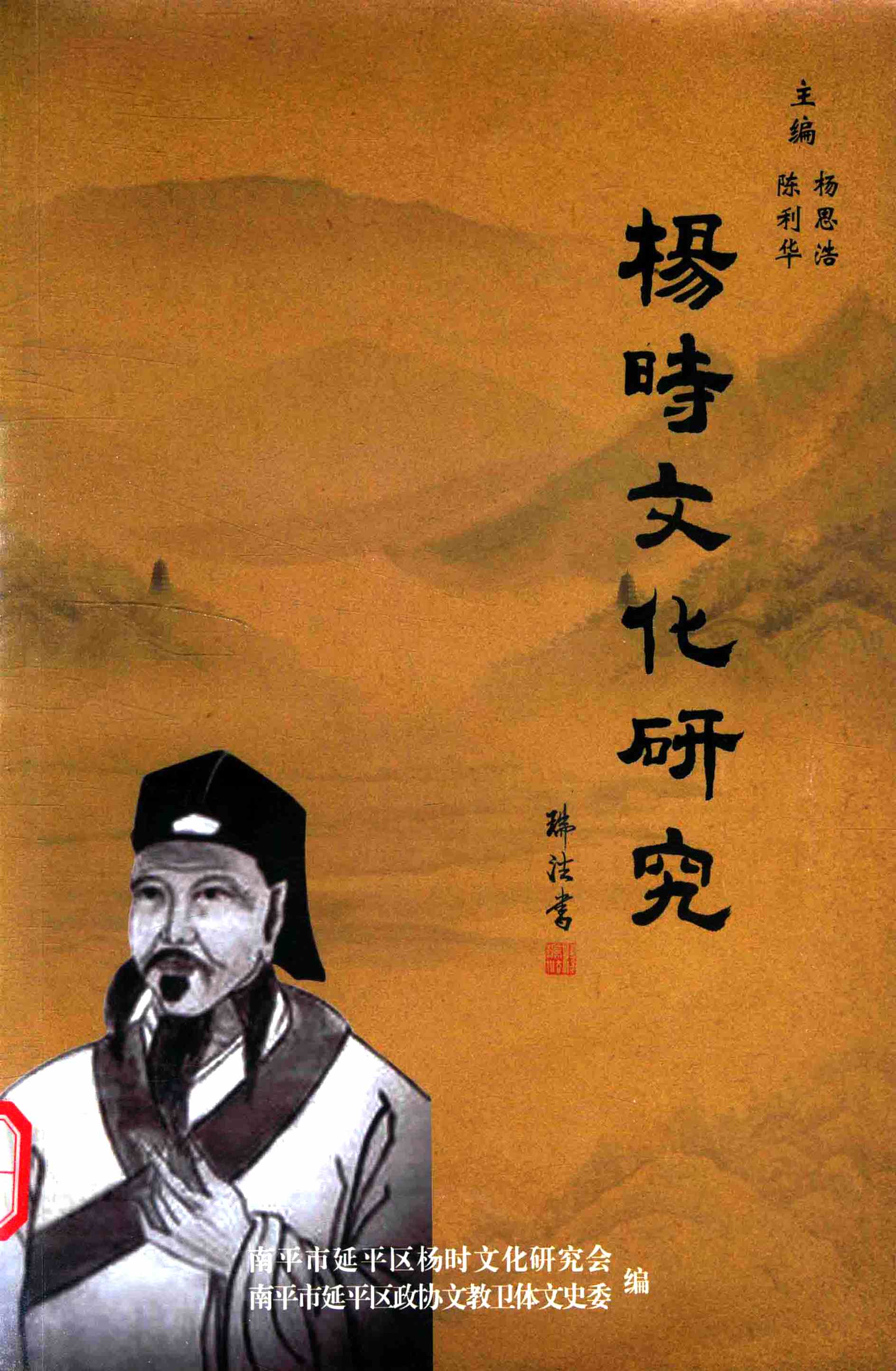内容
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改字中立,生于宋仁宗皇裕五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享年83岁。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三明市)人。洛学南传开道南一脉,至朱熹理学集其大成,“程门高弟”杨时功不可没,后世学者称“龟山先生”。
一、中庸思想是杨时道传东南的主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河南属于中原地区,在隋唐前是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东南一隅,地处偏远,虽中国的经济已逐渐南移,但文化还是不如中原地区。杨时道传东南,为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保存中原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南宋以来,北方连年战争,加上文化远远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高压统治,极大地影响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而南宋政权虽偏安东南,但以华夏正统,重视士大夫阶层,并以“返回三代”为己任,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杨时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原地区的河洛之学从北方传到了南方,为文化中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从历史看,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两次大变迁:一次是从西部往东部转移,这是发生在春秋时期,孔子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一次是从中原转移到东南,为洛学嬗变为闽学提供了基础。问题的关键是这次传统文化的变迁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何重大意义呢?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从末中断,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地理上,二是从学术意义上,人们往往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学术的地理变迁这是至今在学术界很少研究的课题,因此这个“从未中断”均表现为两方面的意义:在地理上,由于战乱或其它的原因,传统文化在中国某个地域中断或消失了,然而却又在中国境内某个地方重新振兴,虽以某种方式或面貌出现,但其核心理念还没改变,而以更新的面貌和更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形态需要出现,这当然需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在这个变迁的链条中,杨时无疑是真正的开创者。在思想史和技术史上,楚才晋用的现象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如佛教诞生在印度而兴盛于中国就是一例,但这期间,承接薪火相传的人相当重要,而杨时就起着传统文化“取经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三个作用,一是使即将消失的文化重新崛起,二是促进“取经者”居住地的文化繁荣,三是为以后的文化集大成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龟山学案》载:“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此事《宋史》也有明确的记载:(杨)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宋史》道学二,第3623页)杨时在二程兄弟在河洛讲解孔孟绝学就前往拜师,并且“相得甚欢”。
在“二程兄弟处”住的时间不算短,并行了敬师礼,当杨时离去时,程颢才会说:“吾道南矣。”杨时四十岁时,又拜见了程颐,在此学习了一段时间。由此可见,杨时在河南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时常来往程门,至于“程门立雪”的故事,只是杨时多次往返程门一次而已,并非传说中杨时和游酢只见一次就戏剧化地“传道东南”了。所以杨时首先是“二程”的高徒,与其师有深刻的交流,并且颇有心得和造诣。正是杨时对程门的思想有着独特的体会和创新,成为了把洛学传往东南的开创者。朱熹理学推二程为正宗,很大程度上是杨时的贡献,二程在河南讲学,弟子众多,杨时是程门得意弟子之一。杨时把“道”传给罗从彦,再传李侗,最后经朱熹集大成,在中华传统文化转型中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杨时也并非全部接受二程的思想体系而是有所创新,其传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就是杨时的哲学思想核心。他抓住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并加以发扬,成功地创新了中庸思想的理论体系,直接地影响了罗从彦。如他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思想以及“已发未发之辩”成为道南之脉绵延不绝的主要议题,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并贯穿道南一脉主体思想。此外,他的“天命即理”等思想也影响着朱熹等宋代大儒本体论建构。
二、中庸理论是杨时哲学思想的核心杨时承二程其学尤重《中庸》,其哲学思想核心是“中庸”。中庸起源于“中”,按照杨时的解释,“中”是实在的,“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龟山文集·语录》)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论述道统时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杨时说“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题中庸后示陈知默》,《杨时集》卷二六)他追述二程遗训“传先生之奥”,这个“奥”在杨时看来是“中庸”。杨时“中庸”思想以天理为超越的形而之上的根据,认为天命即性即理且完备于物我,而且是涵盖了一切儒家德目的“德性”之体(也即是“诚”),成就“德性”之过程和行为之道则是“诚意”。它以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对儒家道德作形上思辨,不仅确立了儒家道德的必要性、可为性、自律性,而且由此进发凸显儒家道德修养以“诚意”为根本。杨时认为《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中庸义序》,《杨时集》卷二五)即把《中庸》视为关乎道德的大学问。朱熹《中庸章句》说“(《中庸》)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杨时)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第一章)清晰概括了杨时“中庸”思想的根本要点,即认为道德的形上根据备于自身,通过自我反身内求而获得,这样便可以去外诱之私,扩充人的本然善性,实现人之道德境界。
中庸之说,无论是杨时或者朱熹(或者说朱熹继承了杨时的思想精髓)都认为中庸的思想缘于上古圣王精传之学。杨时在任朝廷秘书郎时上奏皇帝说: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
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宋史》道学二,第3623页)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朱熹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把中庸之道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庸思想既是当时人民对自然和社会的审视结果,又是对人们对自身所在的地位态度和定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和终极思考,也是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最具有特色的民族性格。中庸的思想是一种“贵和”的思想,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意思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能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最高理想状态,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高级哲理,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思想也就是贵和尚中的思想,既适合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符合了中国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无论是孔孟、二程,以及在此之后的朱熹,都是以“中”为度,以“和”为归结,只不过是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学在和谐理论的不同表现而已。中庸思想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积极作用和对历史影响还是正面的,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多民族政权的维护和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三、杨时中庸思想的落实:以“诚”为核心的功夫论杨时提倡“中庸”,也强调对中庸的体认和实践,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二程洛学的思想宗旨是要确立起具有普遍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即天理,从而使之成为人类生存的依据。格物穷理则是人们把握天理的基本方法,而如何格物穷理便是洛学中人所要探究的问题。
杨时以自己的哲学视角,将格物界定为反身而诚,进一步的落实便是诚意而体中。把洛学的思想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从而把握“中庸”的思想体认和实践,但是这一点和朱熹有很大的不同。“反身而诚”是原始儒家“反求诸己”思想的继承,杨时把握这一思想,并把他与二程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反身而诚”。不唯如此,杨时还认为“诚”就是天、就是道,就是这个“德性”之体。他说“诚者,天之道。诚即天也,故其天其渊。”(《中庸辑略》卷下)“诚”这个“德性”之体将天地万物贯穿起来,可以说万物一体在“诚”。这样“诚”则成为杨时“中庸”哲学思想的核心,所以他说“《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日‘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同上)这个“诚”是就道德形上根据而言的,说的是其至处,杨时说“《论语》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事,莫非诚也,《中庸》言其至也。”(同上)而从道德实践过程和道德行为看,成就“诚”的神道、不二之道就是“诚意”。他说“所谓神道,诚意而已。诚意,天德也”(《语录二·余杭所闻》,《杨时集》卷十一),“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上渊圣皇帝》,《杨时集》卷一)这样“诚意”成为杨时身修平天下的核心,由此凸显了以“诚意”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工夫和路径。不论是其注重“体验未发”和“反身而诚”的内向工夫,还是“格物穷理”的外向工夫,其核心在“诚意”,而“诚意”则将向内和向外成就“德性”的两种路向和工夫合通,使物我之分不复存在,内外之道通合。“大学自正心诚意至治国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这样,按照杨时的思想,“中”是实在的,“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龟山文集语录》)而这个“中”,正是“诚”,是天之道。只是对这个天之道的把握,需要落实在人心,更具体地说,是落实在人心的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这个未发之际便是“诚”在人心的体现,这个体现也被称之为“中”。(参见《龟山文集答学者》)因此,当杨时将格物界定为反身而体会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时,实际上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致知的工夫,知的对象既是指落在人心的性体,同时这性体也是通向形而上之理的金光大道。朱熹曾赞道:“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的中庸理论是以“中庸”理论为基础,以“礼”为标准,强调“礼”对“和”的制约和指导作用,着重以外在制度设施来维护和谐局面的理论形态。这种礼制来维护“中和”的理论一方面具有实践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保守的和谐论。而杨时强调“内心的自觉遵守”,从自觉的态度去维护和谐,这种内向修养的意义更具有强制力和自觉力。杨时提出“诚”的理念,使人们抓住了中庸理论的实践着力点。修养论在古代均体现为功夫论,从内心世界去寻找和谐,提高人们的修养,这是杨时中庸理论的一大特点,可使人们通过修养(功夫)达到内心的和谐,又从内心的和谐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从个人内心的和谐来达到外部的和谐,对我们当今社会道德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杨时中庸思想的本体依据:天理杨时强调内心和谐的“反身而诚”,并寻找它的本体依据,在这方面与他的老师二程有不同之处。二程批评张载作为万物之源的“气”,只不过是物质性的“器”,他们认为“气”有生有灭,只是“理”产生出来的一种暂时性的东西。杨时则不然,他注重对张载气化说的吸收,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杨时还把古来已知的“天命”重新进行了哲理性的解释。杨时说天惠万物,天地养育万物的一切也都是天之所惠,那聪明教民、授民常产、使民衣食的元后也是继天而为天之子。总之,天地万物及万物生养的一切条件都为天之所惠,一切来源于天。而且龟山指出,天命是支配人生的一种为人们所不能抗拒和违背的神秘力量,具有必然性。他说:“圣人未尝不欲道之兴,以无可奈何故委之于命。”“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听之,人自不能违耳。”(《语录一·荆州所闻》,《杨时集》卷十)建构起一个超越而内在的、完备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之身且是他们形上根据的“德性”之体,指出世间的一切都是“德性”的存在。这样他就既因其为儒家的道德实践安立起一个道德的形上根据,确立了道德实践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也因其相信这个“德性”之体完全具备于天地、物我,指明了道德实践的可为性、自律性。在杨时看来:一是天命、人性、人的行为,其体为同一“德性”之体,而这种“德性”之体具超越性、主宰性、普遍性,因而人的“德性”行为当然具必要性、普遍性、合理性,即确立了道德实践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二是这个“德性”之体完全具备于天地、物我,那么在人的“德性”行为过程中,既可以向外物求索,也可以向己身探求,都有可能成就其“德性”。这样既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可为性,以及它的路向,更因其“可以向己身探求”,揭示了道德实践的自律性以及从内心和谐达到外在和谐的必然性。
正因为杨时认识到天命的支配性、无法抗拒性、不可违背性,所以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语录三·余杭所闻》,《杨时集》卷十二),叫人要“事天”、“知天命”、“畏天命”,“人只为不知命,故才有些事,便自劳攘,若知的彻,便于事无不安。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尝解云:‘使孔子不免于桓魋之难,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盖圣人之于命如此。’”(同上)值得注意的是,杨时将这种具超越性、神秘性、主宰性的外在天命和“理”、“天理”联系起来。他说“命,天理也”(《中庸辑略》卷上),“天理即所谓命”(《语录三·余杭所闻》,《杨时集》卷十二)。他把“天命”纳入他“天理”的轨道,认为命就是天理,天理就是命。因此他认为“事天”、“知天”就是要“循天理”,“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同上)杨时在“天命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理论化为“天理论”。二程以一个“自家体帖出来”的“天理”,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为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杨时继承了二程的基本思想,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理”(天理)也是一个有形上特性的哲学范畴。杨时说:“天下只是一个理”,“天理之常,非往非来,虽寿夭兮何伤!”(《语录一·荆州所闻》,《杨时集》卷十)杨时认为“天理”是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的,人有寿命的长短,“天理”却是永世长存的。
这和二程所谓“理”与荀子说“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说法是同一个意思,都是表达了“理”是一个有形上特性的哲学范畴。
杨时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理”,“有物必有则”。(《语录四·南都所闻》,《杨时集》卷一三)这一宇宙变生的“理”存在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自身。他说:“盖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易即是“理”),不知自求,只于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同上)而且这个“理”完全具备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自身,不是物我兼体,而是即我即物即理,“万物与我为一”,“不是我物兼体,若物我兼体则固一,即已即物可谓一矣”。(《语录四·萧山所闻》,《杨时集》卷十三)“物我为一”,不是物和我兼这个体(“理”),而是这个“理”体既是我的,也是他物的,完全具备于物和我,物我一体不二。
同时他还指出,万物变生是同时发生的,有则俱有,并无先后秩序。他说“夫五行在天地之间,有则俱有,故曰阙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后有火,有火然后有木……”(《语录一·荆州所闻》,《杨时集》卷十)“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夫四体与生俱生,身体不备,谓之不成人。阙一不可,亦无先后之次。’”(同上)更为突出的是,他甚至认为这些变生的万物都是“理”。“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语录四·南都所闻》,《杨时集》卷十三)进而他指出,“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同上)也就是说,物本身就是“理”,物是形色,也是天性,形色天性一体。
因此,在杨时的哲学理论中,性、命一体皆为天理,这个天理是超越而内在的,完全具备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自身且是他们的形上根据。他特别强调万物和天理、天与人、形色与天性的一体不二,认为天地万物本身都是“理”。综上观之,杨时谈性、命、天理甚至天地万物一体,物我为一,天地万物即性即命即天理,它们之间不是谁生成谁,而是同体不二。因此不是宇宙生成论的思维模式,很明显是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来谈万物和天理、天与人、形色与天性的“一体不二”。
由此观之,杨时的“反身而诚”而求“中庸”的理论是建立在其“天命”的哲学基础之上,“天地万物一体,物我为一”的“一体不二”的理念确立了杨时反身而诚的哲学观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结语过去,学术界在杨时的传道东南中,较多关注朱熹思想对杨时、罗从彦、李侗思想的“集大成”,没有关注作为“道南一脉”开创者杨时对“二程”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以及杨时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创建。杨时在中庸思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他之所以能够传道东南的基本条件,也是他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吸引了后人学习的兴趣,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需求。杨时“反身求诚”的功夫论不仅影响着朱熹,还影响着王阳明,乃至近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当今社会道德价值观的重建起着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系南平市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一、中庸思想是杨时道传东南的主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河南属于中原地区,在隋唐前是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东南一隅,地处偏远,虽中国的经济已逐渐南移,但文化还是不如中原地区。杨时道传东南,为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保存中原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南宋以来,北方连年战争,加上文化远远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高压统治,极大地影响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而南宋政权虽偏安东南,但以华夏正统,重视士大夫阶层,并以“返回三代”为己任,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杨时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原地区的河洛之学从北方传到了南方,为文化中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从历史看,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两次大变迁:一次是从西部往东部转移,这是发生在春秋时期,孔子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一次是从中原转移到东南,为洛学嬗变为闽学提供了基础。问题的关键是这次传统文化的变迁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何重大意义呢?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从末中断,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地理上,二是从学术意义上,人们往往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学术的地理变迁这是至今在学术界很少研究的课题,因此这个“从未中断”均表现为两方面的意义:在地理上,由于战乱或其它的原因,传统文化在中国某个地域中断或消失了,然而却又在中国境内某个地方重新振兴,虽以某种方式或面貌出现,但其核心理念还没改变,而以更新的面貌和更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形态需要出现,这当然需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在这个变迁的链条中,杨时无疑是真正的开创者。在思想史和技术史上,楚才晋用的现象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如佛教诞生在印度而兴盛于中国就是一例,但这期间,承接薪火相传的人相当重要,而杨时就起着传统文化“取经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三个作用,一是使即将消失的文化重新崛起,二是促进“取经者”居住地的文化繁荣,三是为以后的文化集大成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龟山学案》载:“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此事《宋史》也有明确的记载:(杨)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宋史》道学二,第3623页)杨时在二程兄弟在河洛讲解孔孟绝学就前往拜师,并且“相得甚欢”。
在“二程兄弟处”住的时间不算短,并行了敬师礼,当杨时离去时,程颢才会说:“吾道南矣。”杨时四十岁时,又拜见了程颐,在此学习了一段时间。由此可见,杨时在河南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时常来往程门,至于“程门立雪”的故事,只是杨时多次往返程门一次而已,并非传说中杨时和游酢只见一次就戏剧化地“传道东南”了。所以杨时首先是“二程”的高徒,与其师有深刻的交流,并且颇有心得和造诣。正是杨时对程门的思想有着独特的体会和创新,成为了把洛学传往东南的开创者。朱熹理学推二程为正宗,很大程度上是杨时的贡献,二程在河南讲学,弟子众多,杨时是程门得意弟子之一。杨时把“道”传给罗从彦,再传李侗,最后经朱熹集大成,在中华传统文化转型中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杨时也并非全部接受二程的思想体系而是有所创新,其传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就是杨时的哲学思想核心。他抓住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并加以发扬,成功地创新了中庸思想的理论体系,直接地影响了罗从彦。如他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思想以及“已发未发之辩”成为道南之脉绵延不绝的主要议题,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并贯穿道南一脉主体思想。此外,他的“天命即理”等思想也影响着朱熹等宋代大儒本体论建构。
二、中庸理论是杨时哲学思想的核心杨时承二程其学尤重《中庸》,其哲学思想核心是“中庸”。中庸起源于“中”,按照杨时的解释,“中”是实在的,“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龟山文集·语录》)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论述道统时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杨时说“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题中庸后示陈知默》,《杨时集》卷二六)他追述二程遗训“传先生之奥”,这个“奥”在杨时看来是“中庸”。杨时“中庸”思想以天理为超越的形而之上的根据,认为天命即性即理且完备于物我,而且是涵盖了一切儒家德目的“德性”之体(也即是“诚”),成就“德性”之过程和行为之道则是“诚意”。它以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对儒家道德作形上思辨,不仅确立了儒家道德的必要性、可为性、自律性,而且由此进发凸显儒家道德修养以“诚意”为根本。杨时认为《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中庸义序》,《杨时集》卷二五)即把《中庸》视为关乎道德的大学问。朱熹《中庸章句》说“(《中庸》)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杨时)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第一章)清晰概括了杨时“中庸”思想的根本要点,即认为道德的形上根据备于自身,通过自我反身内求而获得,这样便可以去外诱之私,扩充人的本然善性,实现人之道德境界。
中庸之说,无论是杨时或者朱熹(或者说朱熹继承了杨时的思想精髓)都认为中庸的思想缘于上古圣王精传之学。杨时在任朝廷秘书郎时上奏皇帝说: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
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宋史》道学二,第3623页)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朱熹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把中庸之道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庸思想既是当时人民对自然和社会的审视结果,又是对人们对自身所在的地位态度和定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和终极思考,也是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最具有特色的民族性格。中庸的思想是一种“贵和”的思想,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意思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能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最高理想状态,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高级哲理,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思想也就是贵和尚中的思想,既适合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符合了中国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无论是孔孟、二程,以及在此之后的朱熹,都是以“中”为度,以“和”为归结,只不过是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学在和谐理论的不同表现而已。中庸思想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积极作用和对历史影响还是正面的,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多民族政权的维护和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三、杨时中庸思想的落实:以“诚”为核心的功夫论杨时提倡“中庸”,也强调对中庸的体认和实践,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二程洛学的思想宗旨是要确立起具有普遍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即天理,从而使之成为人类生存的依据。格物穷理则是人们把握天理的基本方法,而如何格物穷理便是洛学中人所要探究的问题。
杨时以自己的哲学视角,将格物界定为反身而诚,进一步的落实便是诚意而体中。把洛学的思想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从而把握“中庸”的思想体认和实践,但是这一点和朱熹有很大的不同。“反身而诚”是原始儒家“反求诸己”思想的继承,杨时把握这一思想,并把他与二程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论联系起来,提出了“反身而诚”。不唯如此,杨时还认为“诚”就是天、就是道,就是这个“德性”之体。他说“诚者,天之道。诚即天也,故其天其渊。”(《中庸辑略》卷下)“诚”这个“德性”之体将天地万物贯穿起来,可以说万物一体在“诚”。这样“诚”则成为杨时“中庸”哲学思想的核心,所以他说“《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日‘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同上)这个“诚”是就道德形上根据而言的,说的是其至处,杨时说“《论语》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事,莫非诚也,《中庸》言其至也。”(同上)而从道德实践过程和道德行为看,成就“诚”的神道、不二之道就是“诚意”。他说“所谓神道,诚意而已。诚意,天德也”(《语录二·余杭所闻》,《杨时集》卷十一),“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上渊圣皇帝》,《杨时集》卷一)这样“诚意”成为杨时身修平天下的核心,由此凸显了以“诚意”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工夫和路径。不论是其注重“体验未发”和“反身而诚”的内向工夫,还是“格物穷理”的外向工夫,其核心在“诚意”,而“诚意”则将向内和向外成就“德性”的两种路向和工夫合通,使物我之分不复存在,内外之道通合。“大学自正心诚意至治国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这样,按照杨时的思想,“中”是实在的,“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龟山文集语录》)而这个“中”,正是“诚”,是天之道。只是对这个天之道的把握,需要落实在人心,更具体地说,是落实在人心的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这个未发之际便是“诚”在人心的体现,这个体现也被称之为“中”。(参见《龟山文集答学者》)因此,当杨时将格物界定为反身而体会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时,实际上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致知的工夫,知的对象既是指落在人心的性体,同时这性体也是通向形而上之理的金光大道。朱熹曾赞道:“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的中庸理论是以“中庸”理论为基础,以“礼”为标准,强调“礼”对“和”的制约和指导作用,着重以外在制度设施来维护和谐局面的理论形态。这种礼制来维护“中和”的理论一方面具有实践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保守的和谐论。而杨时强调“内心的自觉遵守”,从自觉的态度去维护和谐,这种内向修养的意义更具有强制力和自觉力。杨时提出“诚”的理念,使人们抓住了中庸理论的实践着力点。修养论在古代均体现为功夫论,从内心世界去寻找和谐,提高人们的修养,这是杨时中庸理论的一大特点,可使人们通过修养(功夫)达到内心的和谐,又从内心的和谐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从个人内心的和谐来达到外部的和谐,对我们当今社会道德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杨时中庸思想的本体依据:天理杨时强调内心和谐的“反身而诚”,并寻找它的本体依据,在这方面与他的老师二程有不同之处。二程批评张载作为万物之源的“气”,只不过是物质性的“器”,他们认为“气”有生有灭,只是“理”产生出来的一种暂时性的东西。杨时则不然,他注重对张载气化说的吸收,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杨时还把古来已知的“天命”重新进行了哲理性的解释。杨时说天惠万物,天地养育万物的一切也都是天之所惠,那聪明教民、授民常产、使民衣食的元后也是继天而为天之子。总之,天地万物及万物生养的一切条件都为天之所惠,一切来源于天。而且龟山指出,天命是支配人生的一种为人们所不能抗拒和违背的神秘力量,具有必然性。他说:“圣人未尝不欲道之兴,以无可奈何故委之于命。”“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听之,人自不能违耳。”(《语录一·荆州所闻》,《杨时集》卷十)建构起一个超越而内在的、完备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之身且是他们形上根据的“德性”之体,指出世间的一切都是“德性”的存在。这样他就既因其为儒家的道德实践安立起一个道德的形上根据,确立了道德实践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也因其相信这个“德性”之体完全具备于天地、物我,指明了道德实践的可为性、自律性。在杨时看来:一是天命、人性、人的行为,其体为同一“德性”之体,而这种“德性”之体具超越性、主宰性、普遍性,因而人的“德性”行为当然具必要性、普遍性、合理性,即确立了道德实践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二是这个“德性”之体完全具备于天地、物我,那么在人的“德性”行为过程中,既可以向外物求索,也可以向己身探求,都有可能成就其“德性”。这样既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可为性,以及它的路向,更因其“可以向己身探求”,揭示了道德实践的自律性以及从内心和谐达到外在和谐的必然性。
正因为杨时认识到天命的支配性、无法抗拒性、不可违背性,所以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语录三·余杭所闻》,《杨时集》卷十二),叫人要“事天”、“知天命”、“畏天命”,“人只为不知命,故才有些事,便自劳攘,若知的彻,便于事无不安。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尝解云:‘使孔子不免于桓魋之难,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盖圣人之于命如此。’”(同上)值得注意的是,杨时将这种具超越性、神秘性、主宰性的外在天命和“理”、“天理”联系起来。他说“命,天理也”(《中庸辑略》卷上),“天理即所谓命”(《语录三·余杭所闻》,《杨时集》卷十二)。他把“天命”纳入他“天理”的轨道,认为命就是天理,天理就是命。因此他认为“事天”、“知天”就是要“循天理”,“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同上)杨时在“天命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理论化为“天理论”。二程以一个“自家体帖出来”的“天理”,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为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杨时继承了二程的基本思想,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理”(天理)也是一个有形上特性的哲学范畴。杨时说:“天下只是一个理”,“天理之常,非往非来,虽寿夭兮何伤!”(《语录一·荆州所闻》,《杨时集》卷十)杨时认为“天理”是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的,人有寿命的长短,“天理”却是永世长存的。
这和二程所谓“理”与荀子说“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说法是同一个意思,都是表达了“理”是一个有形上特性的哲学范畴。
杨时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理”,“有物必有则”。(《语录四·南都所闻》,《杨时集》卷一三)这一宇宙变生的“理”存在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自身。他说:“盖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易即是“理”),不知自求,只于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同上)而且这个“理”完全具备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自身,不是物我兼体,而是即我即物即理,“万物与我为一”,“不是我物兼体,若物我兼体则固一,即已即物可谓一矣”。(《语录四·萧山所闻》,《杨时集》卷十三)“物我为一”,不是物和我兼这个体(“理”),而是这个“理”体既是我的,也是他物的,完全具备于物和我,物我一体不二。
同时他还指出,万物变生是同时发生的,有则俱有,并无先后秩序。他说“夫五行在天地之间,有则俱有,故曰阙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后有火,有火然后有木……”(《语录一·荆州所闻》,《杨时集》卷十)“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夫四体与生俱生,身体不备,谓之不成人。阙一不可,亦无先后之次。’”(同上)更为突出的是,他甚至认为这些变生的万物都是“理”。“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语录四·南都所闻》,《杨时集》卷十三)进而他指出,“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同上)也就是说,物本身就是“理”,物是形色,也是天性,形色天性一体。
因此,在杨时的哲学理论中,性、命一体皆为天理,这个天理是超越而内在的,完全具备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自身且是他们的形上根据。他特别强调万物和天理、天与人、形色与天性的一体不二,认为天地万物本身都是“理”。综上观之,杨时谈性、命、天理甚至天地万物一体,物我为一,天地万物即性即命即天理,它们之间不是谁生成谁,而是同体不二。因此不是宇宙生成论的思维模式,很明显是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来谈万物和天理、天与人、形色与天性的“一体不二”。
由此观之,杨时的“反身而诚”而求“中庸”的理论是建立在其“天命”的哲学基础之上,“天地万物一体,物我为一”的“一体不二”的理念确立了杨时反身而诚的哲学观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结语过去,学术界在杨时的传道东南中,较多关注朱熹思想对杨时、罗从彦、李侗思想的“集大成”,没有关注作为“道南一脉”开创者杨时对“二程”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以及杨时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创建。杨时在中庸思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他之所以能够传道东南的基本条件,也是他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吸引了后人学习的兴趣,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需求。杨时“反身求诚”的功夫论不仅影响着朱熹,还影响着王阳明,乃至近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当今社会道德价值观的重建起着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系南平市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相关人物
吴吉民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