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侗对朱熹《论语》思想的影响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66 |
| 颗粒名称: | 一、李侗对朱熹《论语》思想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6 |
| 页码: | 263-268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首先李侗对朱熹《论语》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强调《论语》的工夫论上。其次,李侗推动和完善了《论语》原有范畴的理学化。 |
| 关键词: | 李侗 朱熹 《论语》 |
内容
朱熹对《论语》的重视和精读在初见李侗后就开始了,他在同安任职期间,曾抽空到县学把《论语》讲授一遍,试图在本县树立“为己之学”的学风。他自己更是时刻不忘研读、思考《论语》。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出差到德化时,一度通宵达旦思考“子夏门人小子”章,领悟到“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的道理:。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月到十月间,朱熹在同安的畏垒庵精读《论语》、《孟子》,并将自己的读书体会以札记形式记录下来。后来每次拜见李侗归后,都要写信问及《论语》。据统计,在《延平答问》中,二人答问共计六十四条,其中明确讨论《论语》的有二十一条,涉及某些章节的文义、古注、理学义涵等内容。其实,《论语》本是宋代理学家普遍重视的经典,道南一系的开山——杨时也非常看重《论语》,当胡宏向杨时问为学之方时,杨时只是告诉他:“且看《论语》。”李侗亦是如此。朱熹说:“李先生好看《论语》,自明而言。”后来朱熹也告诉弟子:“圣人教人,只是个《论语》。”可以说,重视《论语》是从杨时、李侗对朱熹的一贯传统。
李侗对朱熹《论语》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强调《论语》的工夫论上。李侗告诉朱熹:“《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后来朱熹也一再告诉弟子,《论语》“但云求仁之方”。在李侗和朱熹看来,《论语》重点在做“实事”、做“工夫”,所以朱熹告诉弟子:“《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又说:“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使人便做工夫云,久则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谓‘下学上达’也。”李侗认为学者应从日用工夫中去体会《论语》,而不是执着于高妙之说来注解《论语》。朱熹在一封信中说:“伯崇去年春间得书,问《论语》数段,其说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为不然,令其悫实做工夫。后来便别。”在李侗的影响下,朱熹终生注重《论语》所谈的“涵养”工夫,绝不轻易谈论“圣贤气象”。他说:“《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如《论语》所言‘居处薛,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类,皆是存养底意思。”又说:“向时朋友只管爱说曾点漆雕开优劣,亦何必如此。但当思量我何缘得到漆雕开田地,何缘得到曾点田地。若不去学他做,只管较他优劣,便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
其次,李侗推动和完善了《论语》原有范畴的理学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有两处,一是将“吾道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二是用天理来解说“仁”字。
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往见李侗之前,朱熹已经在同胡宪、范如圭等书信往来论辨“一贯”之说。胡宪认为一道贯忠恕,从理上看,忠恕非二,朱熹深表赞同,说:“此语深符鄙意。盖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哉!忠恕盖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则在言外矣。”后来朱熹拜见李侗时又问“一贯”,他说:“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见谓忠恕正曾子见处,及门人有问,则亦以其所见谕之而已,岂有二言哉!熹复问以近世儒者之说如何,曰:‘如此则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适与卑意不约而合。”拜见李侗归后,他在给范如圭的两封信中,进一步讨论“一贯”、“忠恕”,他说:“前书所论忠恕则一,而在圣人、在学者,则不能无异……熹之言亦非谓忠恕为有二也。”又说:“盖忠恕二字,自众人观之,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盖既曰一贯,则无小大之殊故也。”此时朱熹认为忠恕为一,尽管在现实中存在“众人”和“圣人”的差异,但就“一贯”而言,并无“小大之殊”。显然这里已经蕴含了理一分殊的理念,只是没有明确表达而已。
在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中,朱熹就“一贯”、“忠恕”告诉李侗:“盖以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有贯之者,未尝不一也。然则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门人,岂有异旨哉!”所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有贯之者,未尝不一”,已经明确表达出“理一分殊”的思想。李侗在答书中肯定了朱熹的看法,说:
伊川先生有言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体会于一人之身,不过只是尽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于日用处,夫子自有以见之,恐其未必觉此亦是一贯之理,故卒然问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于是领会而有得焉,辄应之曰:“唯。,”……至于答门人之问,……岂有二耶?若以谓圣人一以贯之之道,其精微非门人之间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是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特起此以示人相近处,然不能贯之,则忠恕自是一忠恕尔。
李侗和朱熹都认为曾子所说的“忠恕”与孔子说“一贯”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一贯”、“忠恕”实际上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后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便用“道”之体用来进一步说明“一贯”、“忠恕”的关系,即“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此处“一本”与“万殊”的表述方式较戊寅书中更加明确了。事实上,朱熹对“一贯”、“忠恕”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晚年,他还对陈淳说:“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要之,朱熹在三十岁时与胡宪、范如圭、李侗对“一贯”、“忠恕”的反复讨论促使其“理一分殊”思想的逐步明朗化,这正是他后来阐述、修订《论语》中“一贯”、“忠恕”看法的基调。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是孔子与弟子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孔子最为看重的德性。任何阅读、注释《论语》者都不能忽视“仁”字,李侗和朱熹亦不例外。在《延平答问》中,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专门讨论“仁”字含义:一方面,李侗一再强调“仁”字难说,必须在日用实践之中去领会。他说:“某尝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另一方面,李侗肯定了朱熹所谓“仁是心之正理”的观点。他说:“来谕以谓仁是心之正理,能发能用底一个端绪,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气无不纯备,而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顷刻停息,愤盈发泄,触处贯通,体用相循,初无间断。此说推扩得甚好。”在辛巳二月十四日书中,李侗论及“殷有三仁”章时指出:“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后来朱熹进一步阐释说:“同谓之仁者,以其皆无私而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与?”可见,朱熹在李侗的“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的启发下,提出仁既有“心之体”又有“心之用”,即为“全心之德”,基于此,“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最终成为朱熹对《论语》中“仁”字的定义,“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
通过与师友的反复讨论,朱熹对《论语》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于是在隆兴元年(1163)上半年编成《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朱熹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说:“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说:“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这里所谓“晚亲”和“师友”,李侗当在其列。而在《论语集注》这部朱熹《论语》学的成熟之作中,朱熹在“吾与回言终日”章直接引用了李侗的话:
愚闻之师曰:“颜子深潜纯粹,其于圣人体段已具。其闻夫子之言,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然后知其不愚也。”
这段对颜子的评价,代表了李侗对圣贤气象的基本观点,影响到朱熹对颜子、曾子、曾点等孔门弟子的评价。另外,朱熹将《延平答问》中的某些答问直接录入《论语或问》当中,以便开示后学。如在戊寅七月十七日书中,朱熹就“父在观其志”章提问:“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类似的问题在《论语或问》中再次呈现:“或曰:昔谢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则以渐变之使无迹可寻。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过有当必改者,以是为法,而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不亦可乎?”接着,朱熹以李侗的话作为回答:“吾尝闻之师矣,以为此其意则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当至诚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隐忍迁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学者用心微矣。”由此可见,李侗在朱熹注释《论语》的过程中起到了直接指导的作用。
李侗对朱熹《论语》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强调《论语》的工夫论上。李侗告诉朱熹:“《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后来朱熹也一再告诉弟子,《论语》“但云求仁之方”。在李侗和朱熹看来,《论语》重点在做“实事”、做“工夫”,所以朱熹告诉弟子:“《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又说:“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使人便做工夫云,久则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谓‘下学上达’也。”李侗认为学者应从日用工夫中去体会《论语》,而不是执着于高妙之说来注解《论语》。朱熹在一封信中说:“伯崇去年春间得书,问《论语》数段,其说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为不然,令其悫实做工夫。后来便别。”在李侗的影响下,朱熹终生注重《论语》所谈的“涵养”工夫,绝不轻易谈论“圣贤气象”。他说:“《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如《论语》所言‘居处薛,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礼勿视听言动’之类,皆是存养底意思。”又说:“向时朋友只管爱说曾点漆雕开优劣,亦何必如此。但当思量我何缘得到漆雕开田地,何缘得到曾点田地。若不去学他做,只管较他优劣,便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
其次,李侗推动和完善了《论语》原有范畴的理学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有两处,一是将“吾道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二是用天理来解说“仁”字。
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往见李侗之前,朱熹已经在同胡宪、范如圭等书信往来论辨“一贯”之说。胡宪认为一道贯忠恕,从理上看,忠恕非二,朱熹深表赞同,说:“此语深符鄙意。盖既无有内外边际,则何往而非一贯哉!忠恕盖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则在言外矣。”后来朱熹拜见李侗时又问“一贯”,他说:“熹顷至延平,见李愿中丈,问以‘一贯’、‘忠恕’之说:见谓忠恕正曾子见处,及门人有问,则亦以其所见谕之而已,岂有二言哉!熹复问以近世儒者之说如何,曰:‘如此则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适与卑意不约而合。”拜见李侗归后,他在给范如圭的两封信中,进一步讨论“一贯”、“忠恕”,他说:“前书所论忠恕则一,而在圣人、在学者,则不能无异……熹之言亦非谓忠恕为有二也。”又说:“盖忠恕二字,自众人观之,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盖既曰一贯,则无小大之殊故也。”此时朱熹认为忠恕为一,尽管在现实中存在“众人”和“圣人”的差异,但就“一贯”而言,并无“小大之殊”。显然这里已经蕴含了理一分殊的理念,只是没有明确表达而已。
在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中,朱熹就“一贯”、“忠恕”告诉李侗:“盖以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有贯之者,未尝不一也。然则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门人,岂有异旨哉!”所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有贯之者,未尝不一”,已经明确表达出“理一分殊”的思想。李侗在答书中肯定了朱熹的看法,说:
伊川先生有言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体会于一人之身,不过只是尽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于日用处,夫子自有以见之,恐其未必觉此亦是一贯之理,故卒然问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于是领会而有得焉,辄应之曰:“唯。,”……至于答门人之问,……岂有二耶?若以谓圣人一以贯之之道,其精微非门人之间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是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特起此以示人相近处,然不能贯之,则忠恕自是一忠恕尔。
李侗和朱熹都认为曾子所说的“忠恕”与孔子说“一贯”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一贯”、“忠恕”实际上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后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便用“道”之体用来进一步说明“一贯”、“忠恕”的关系,即“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此处“一本”与“万殊”的表述方式较戊寅书中更加明确了。事实上,朱熹对“一贯”、“忠恕”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晚年,他还对陈淳说:“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要之,朱熹在三十岁时与胡宪、范如圭、李侗对“一贯”、“忠恕”的反复讨论促使其“理一分殊”思想的逐步明朗化,这正是他后来阐述、修订《论语》中“一贯”、“忠恕”看法的基调。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是孔子与弟子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孔子最为看重的德性。任何阅读、注释《论语》者都不能忽视“仁”字,李侗和朱熹亦不例外。在《延平答问》中,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专门讨论“仁”字含义:一方面,李侗一再强调“仁”字难说,必须在日用实践之中去领会。他说:“某尝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另一方面,李侗肯定了朱熹所谓“仁是心之正理”的观点。他说:“来谕以谓仁是心之正理,能发能用底一个端绪,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气无不纯备,而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顷刻停息,愤盈发泄,触处贯通,体用相循,初无间断。此说推扩得甚好。”在辛巳二月十四日书中,李侗论及“殷有三仁”章时指出:“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后来朱熹进一步阐释说:“同谓之仁者,以其皆无私而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与?”可见,朱熹在李侗的“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的启发下,提出仁既有“心之体”又有“心之用”,即为“全心之德”,基于此,“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最终成为朱熹对《论语》中“仁”字的定义,“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
通过与师友的反复讨论,朱熹对《论语》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于是在隆兴元年(1163)上半年编成《论语要义》和《训蒙口义》。朱熹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说:“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说:“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这里所谓“晚亲”和“师友”,李侗当在其列。而在《论语集注》这部朱熹《论语》学的成熟之作中,朱熹在“吾与回言终日”章直接引用了李侗的话:
愚闻之师曰:“颜子深潜纯粹,其于圣人体段已具。其闻夫子之言,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然后知其不愚也。”
这段对颜子的评价,代表了李侗对圣贤气象的基本观点,影响到朱熹对颜子、曾子、曾点等孔门弟子的评价。另外,朱熹将《延平答问》中的某些答问直接录入《论语或问》当中,以便开示后学。如在戊寅七月十七日书中,朱熹就“父在观其志”章提问:“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类似的问题在《论语或问》中再次呈现:“或曰:昔谢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则以渐变之使无迹可寻。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过有当必改者,以是为法,而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不亦可乎?”接着,朱熹以李侗的话作为回答:“吾尝闻之师矣,以为此其意则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当至诚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隐忍迁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学者用心微矣。”由此可见,李侗在朱熹注释《论语》的过程中起到了直接指导的作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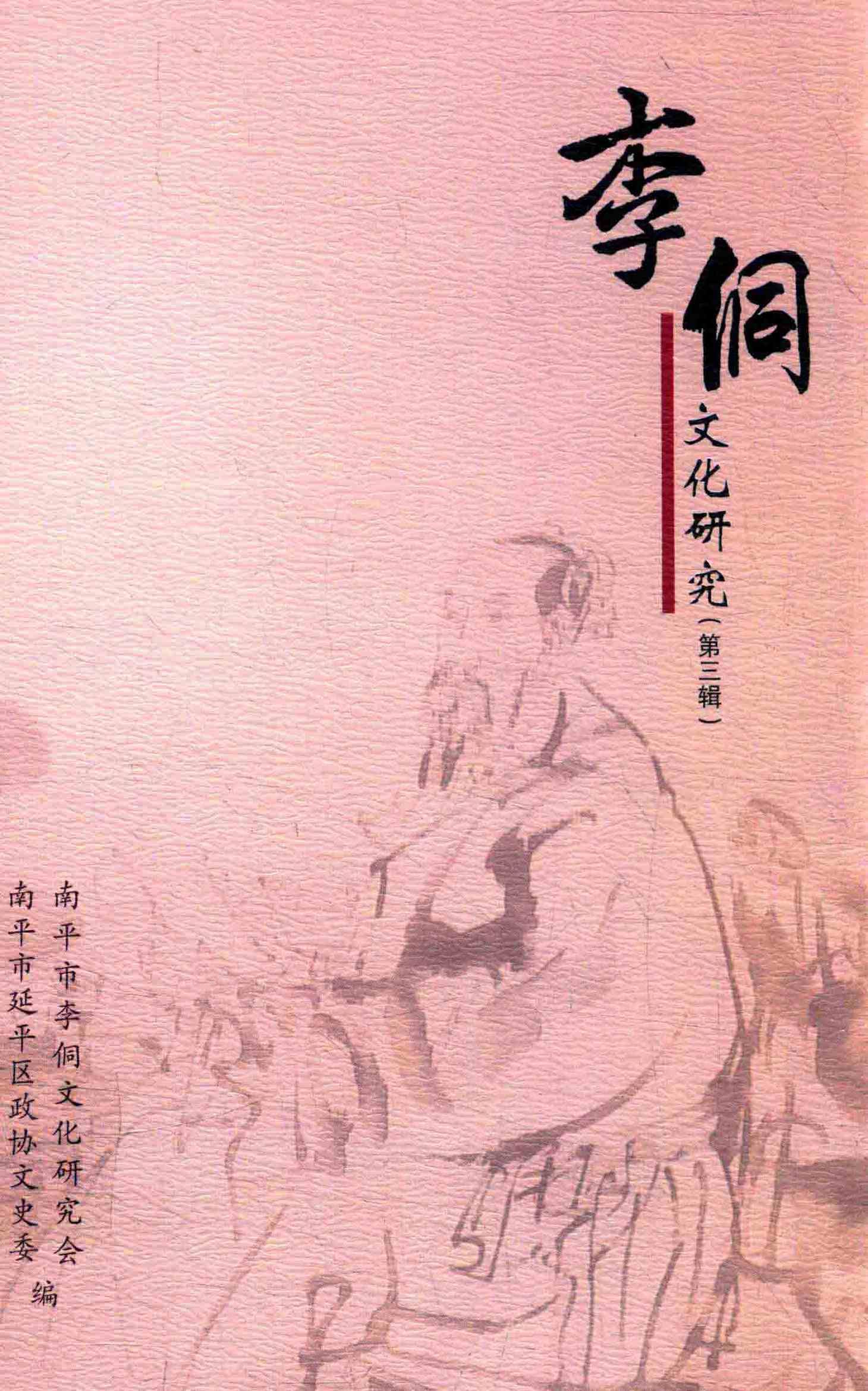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